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台山集卷十七 第 x 页
台山集卷十七(安东金迈淳德叟)
阙馀散笔
阙馀散笔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1H 页
 榕村第三
榕村第三榕村李光地。以经术文章。显用于康熙时。官至太学士。号为中州大儒。今得其全集而读之。易诗诸说。包综赡博。见解敏妙。往往发前未发。语录十卷。商确古今。议论尽多可观。东儒之汨没训诂。依㨾循辙。茫然无一半自得者。诚不足以望其藩篱。而统论学术全体。则长于驰骛而短于持守。谐世适用之意多。而修身敦本之味少耳。其自命儒者。仕不逢时。隐之于心。若有不自得者。而既已濡足。无由转脑。则反欲曲加文饰。硬做义理。故其生于心。发于言者。类多枝梧拖带。不甚快活。试举其一二而言之。如曰文中子于南北朝。夺统归魏。亦有意思。晋灭恰值元魏兴于北。修明礼乐。欲复古制。春秋之法。中国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天意无中外也。又为管夷吾,荀文若。极力分疏曰。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应天顺人。管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1L 页
 仲之事雠。圣人以为仁。又论元会运世。以为由尧至汤。汤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贞观。又五百年而生朱子。自朱子后至我朝。又五百年。盖尊戴康熙。上拟汤文。而毅然自居于伊莱吕散之列也。夫华夷。天地之大分也。君臣。人之大伦也。儒之所以为儒。将以讲明斯义。处两间而参三才也。今乃拘于时势。牵于己私。欲以区区笔舌。漫漶而混沦之。使此老幸而生于宋 明盛际。则其肯为此论耶。天意果无中外。则帝舜何以蛮夷猾夏为忧。仲尼何以不被发左衽为幸乎。放君果皆救民。事雠果皆为仁。则何恶乎曹操,朱温。何诛乎褚渊,冯道。孟子又何以枉尺直寻为不可乎。至若五百年王者之说。孟子特据其已然之迹言之耳。非谓来头废兴。一一准此。如分至启闭之可以坐致千岁也。今为自己伊莱计。援引建武贞观。傅会年数。趁课填额。一以为雍齿之封侯。一以为子孔之立后。而赫赫汤文。遂作媚世取宠之资。儒之见有如是局。而儒之言有如是苟欤。许鲁斋出处。不免后人雌黄。而鲁斋无此等议论。不亦脱洒真悫矣乎。
仲之事雠。圣人以为仁。又论元会运世。以为由尧至汤。汤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贞观。又五百年而生朱子。自朱子后至我朝。又五百年。盖尊戴康熙。上拟汤文。而毅然自居于伊莱吕散之列也。夫华夷。天地之大分也。君臣。人之大伦也。儒之所以为儒。将以讲明斯义。处两间而参三才也。今乃拘于时势。牵于己私。欲以区区笔舌。漫漶而混沦之。使此老幸而生于宋 明盛际。则其肯为此论耶。天意果无中外。则帝舜何以蛮夷猾夏为忧。仲尼何以不被发左衽为幸乎。放君果皆救民。事雠果皆为仁。则何恶乎曹操,朱温。何诛乎褚渊,冯道。孟子又何以枉尺直寻为不可乎。至若五百年王者之说。孟子特据其已然之迹言之耳。非谓来头废兴。一一准此。如分至启闭之可以坐致千岁也。今为自己伊莱计。援引建武贞观。傅会年数。趁课填额。一以为雍齿之封侯。一以为子孔之立后。而赫赫汤文。遂作媚世取宠之资。儒之见有如是局。而儒之言有如是苟欤。许鲁斋出处。不免后人雌黄。而鲁斋无此等议论。不亦脱洒真悫矣乎。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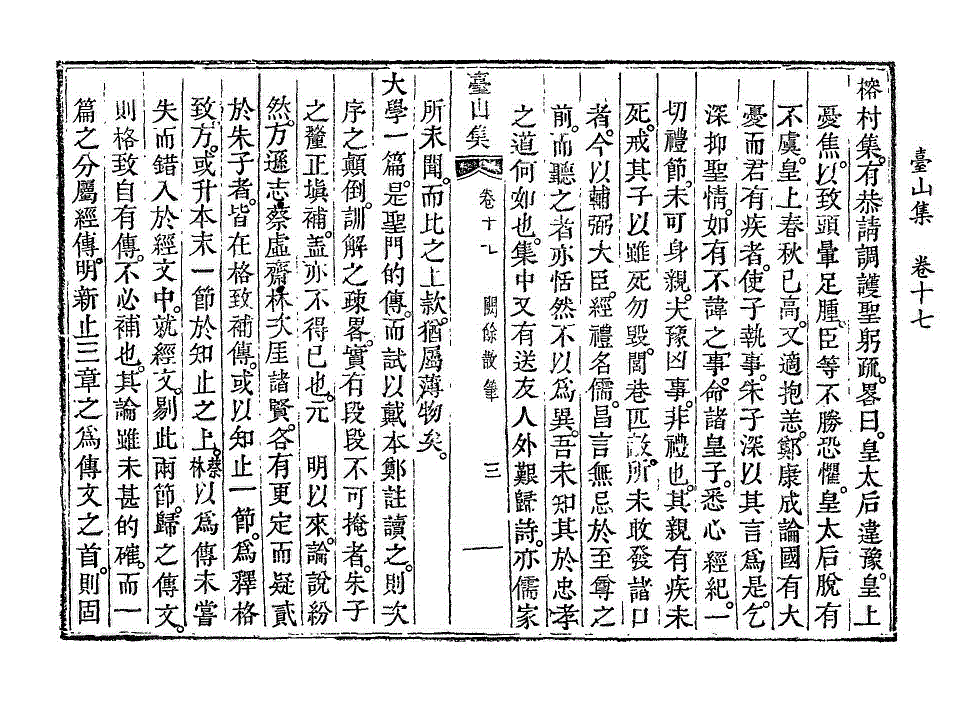 榕村集。有恭请调护圣躬疏。略曰。皇太后违豫。皇上忧焦。以致头晕足肿。臣等不胜恐惧。皇太后脱有不虞。皇上春秋已高。又适抱恙。郑康成论国有大忧而君有疾者。使子执事。朱子深以其言为是。乞深抑圣情。如有不讳之事。命诸皇子。悉心经纪。一切礼节。未可身亲。夫豫凶事。非礼也。其亲有疾未死。戒其子以虽死勿毁。闾巷匹敌。所未敢发诸口者。今以辅弼大臣。经礼名儒。昌言无忌于至尊之前。而听之者亦恬然不以为异。吾未知其于忠孝之道何如也。集中又有送友人外艰归诗。亦儒家所未闻。而比之上款。犹属薄物矣。
榕村集。有恭请调护圣躬疏。略曰。皇太后违豫。皇上忧焦。以致头晕足肿。臣等不胜恐惧。皇太后脱有不虞。皇上春秋已高。又适抱恙。郑康成论国有大忧而君有疾者。使子执事。朱子深以其言为是。乞深抑圣情。如有不讳之事。命诸皇子。悉心经纪。一切礼节。未可身亲。夫豫凶事。非礼也。其亲有疾未死。戒其子以虽死勿毁。闾巷匹敌。所未敢发诸口者。今以辅弼大臣。经礼名儒。昌言无忌于至尊之前。而听之者亦恬然不以为异。吾未知其于忠孝之道何如也。集中又有送友人外艰归诗。亦儒家所未闻。而比之上款。犹属薄物矣。大学一篇。是圣门的传。而试以戴本郑注读之。则次序之颠倒。训解之疏略。实有段段不可掩者。朱子之釐正填补。盖亦不得已也。元 明以来。论说纷然。方逊志,蔡虚斋,林次厓诸贤。各有更定而疑贰于朱子者。皆在格致补传。或以知止一节。为释格致方。或升本末一节于知止之上。(蔡林)以为传未尝失而错入于经文中。就经文。剔此两节。归之传文。则格致自有传。不必补也。其论虽未甚的确。而一篇之分属经传。明新止三章之为传文之首。则固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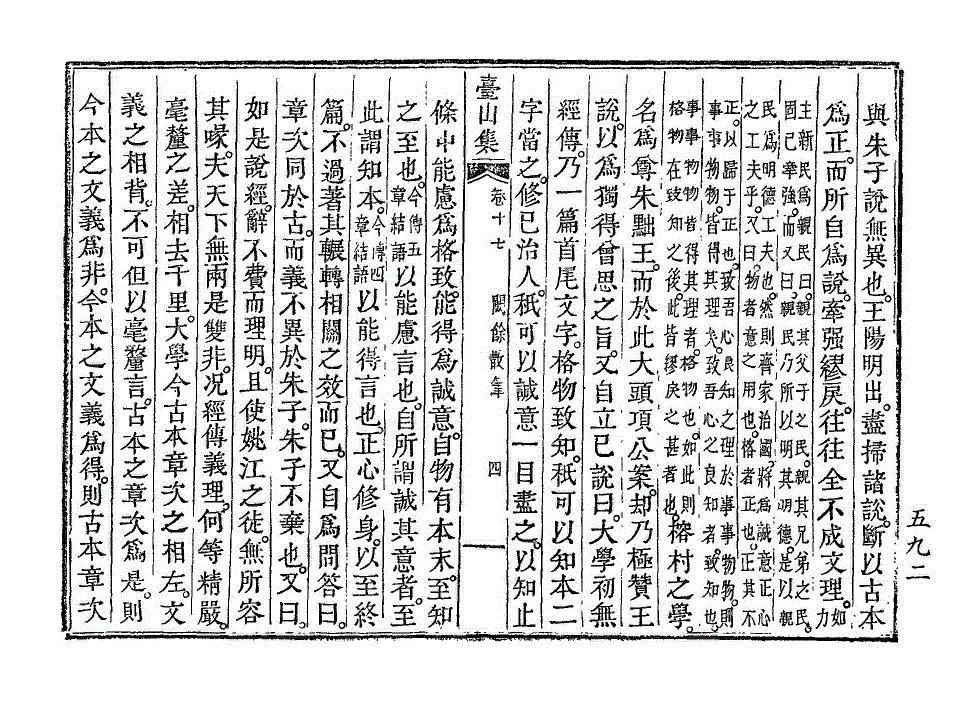 与朱子说无异也。王阳明出。尽扫诸说。断以古本为正。而所自为说。牵强缪戾。往往全不成文理。(如力主新民为亲民曰。亲其父子之民。亲其兄弟之民。固已牵强。而又曰。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是以亲民为明德工夫也。然则齐家治国。将为诚意正心之工夫乎。又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则格物在致知之后。此皆缪戾之甚者也。)榕村之学。名为尊朱黜王。而于此大头项公案。却乃极赞王说。以为独得曾,思之旨。又自立己说曰。大学初无经传。乃一篇首尾文字。格物致知。秖可以知本二字当之。修己治人。秖可以诚意一目尽之。以知止条中能虑为格致。能得为诚意。自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今传五章结语)以能虑言也。自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今传四章结语)以能得言也。正心修身。以至终篇。不过著其辗转相关之效而已。又自为问答曰。章次同于古。而义不异于朱子。朱子不弃也。又曰。如是说经。辞不费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无所容其喙。夫天下无两是双非。况经传义理。何等精严。毫釐之差。相去千里。大学今古本章次之相左。文义之相背。不可但以毫釐言。古本之章次为是。则今本之文义为非。今本之文义为得。则古本章次
与朱子说无异也。王阳明出。尽扫诸说。断以古本为正。而所自为说。牵强缪戾。往往全不成文理。(如力主新民为亲民曰。亲其父子之民。亲其兄弟之民。固已牵强。而又曰。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是以亲民为明德工夫也。然则齐家治国。将为诚意正心之工夫乎。又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则格物在致知之后。此皆缪戾之甚者也。)榕村之学。名为尊朱黜王。而于此大头项公案。却乃极赞王说。以为独得曾,思之旨。又自立己说曰。大学初无经传。乃一篇首尾文字。格物致知。秖可以知本二字当之。修己治人。秖可以诚意一目尽之。以知止条中能虑为格致。能得为诚意。自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今传五章结语)以能虑言也。自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今传四章结语)以能得言也。正心修身。以至终篇。不过著其辗转相关之效而已。又自为问答曰。章次同于古。而义不异于朱子。朱子不弃也。又曰。如是说经。辞不费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无所容其喙。夫天下无两是双非。况经传义理。何等精严。毫釐之差。相去千里。大学今古本章次之相左。文义之相背。不可但以毫釐言。古本之章次为是。则今本之文义为非。今本之文义为得。则古本章次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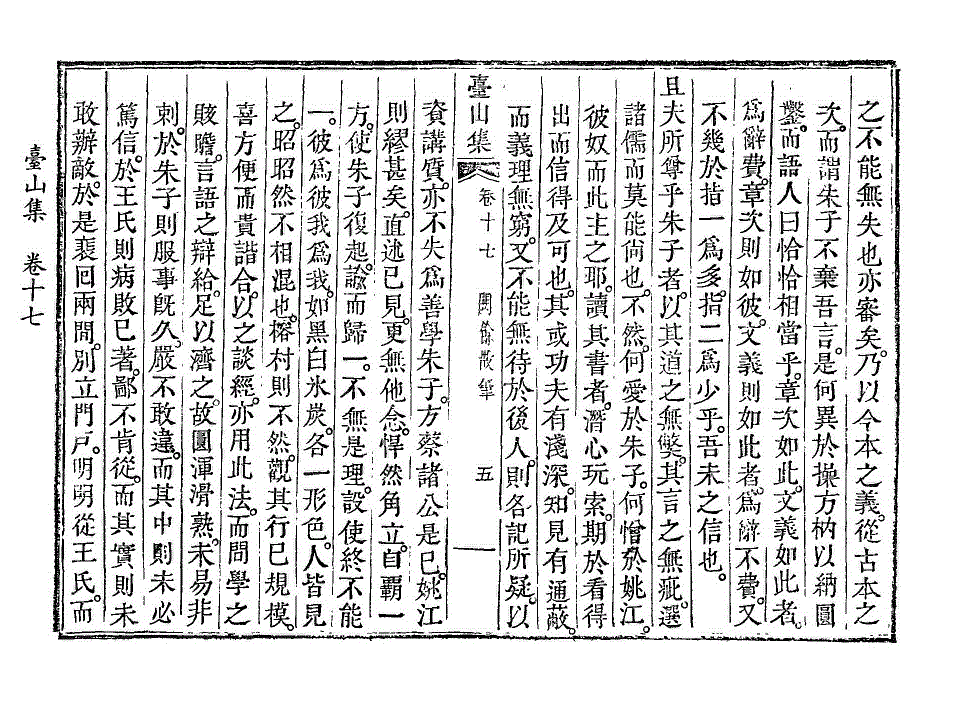 之不能无失也亦审矣。乃以今本之义。从古本之次。而谓朱子不弃吾言。是何异于操方枘以纳圆凿。而语人曰恰恰相当乎。章次如此。文义如此者。为辞费。章次则如彼。文义则如此者。为辞不费。又不几于指一为多。指二为少乎。吾未之信也。
之不能无失也亦审矣。乃以今本之义。从古本之次。而谓朱子不弃吾言。是何异于操方枘以纳圆凿。而语人曰恰恰相当乎。章次如此。文义如此者。为辞费。章次则如彼。文义则如此者。为辞不费。又不几于指一为多。指二为少乎。吾未之信也。且夫所尊乎朱子者。以其道之无弊。其言之无疵。选诸儒而莫能尚也。不然。何爱于朱子。何憎于姚江。彼奴而此主之耶。读其书者。潜心玩索。期于看得出而信得及可也。其或功夫有浅深。知见有通蔽。而义理无穷。又不能无待于后人。则各记所疑。以资讲质。亦不失为善学朱子。方蔡诸公是已。姚江则缪甚矣。直述已见。更无他念。悍然角立。自霸一方。使朱子复起。谕而归一。不无是理。设使终不能一。彼为彼我为我。如黑白冰炭。各一形色。人皆见之。昭昭然不相混也。榕村则不然。观其行己规模。喜方便而贵谐合。以之谈经。亦用此法。而问学之赅赡。言语之辩给。足以济之。故圆浑滑熟。未易非剌。于朱子则服事既久。严不敢违。而其中则未必笃信。于王氏则病败已著。鄙不肯从。而其实则未敢办敌。于是裴回两间。别立门户。明明从王氏。而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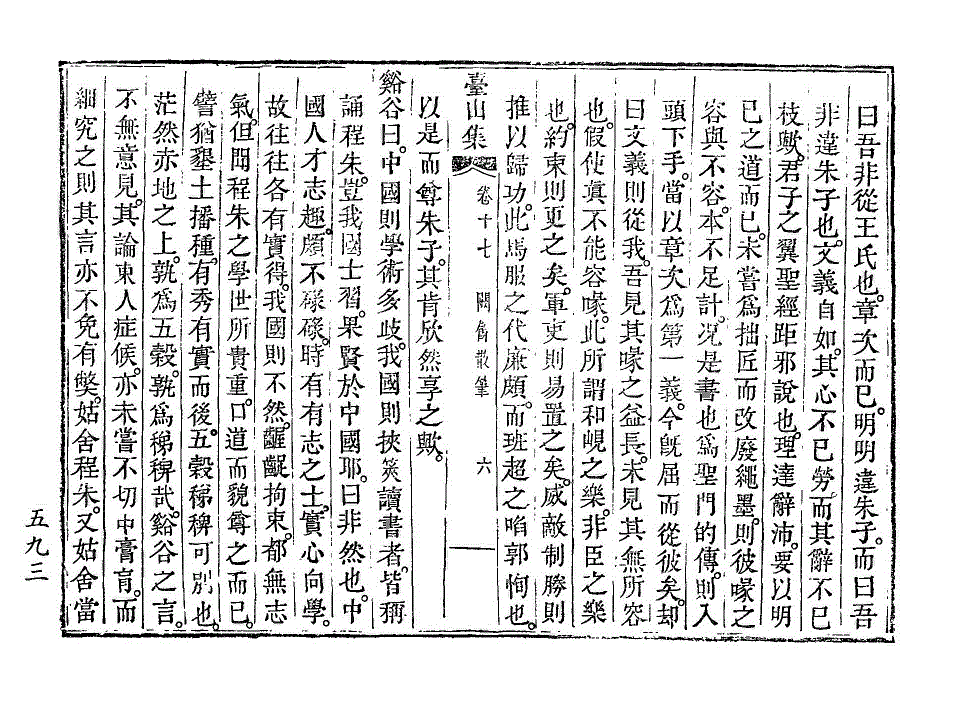 曰吾非从王氏也。章次而已。明明违朱子。而曰吾非违朱子也。文义自如。其心不已劳。而其辞不已枝欤。君子之翼圣经距邪说也。理达辞沛。要以明己之道而已。未尝为拙匠而改废绳墨。则彼喙之容与不容。本不足计。况是书也为圣门的传。则入头下手。当以章次为第一义。今既屈而从彼矣。却曰文义则从我。吾见其喙之益长。未见其无所容也。假使真不能容喙。此所谓和岘之乐。非臣之乐也。约束则更之矣。军吏则易置之矣。威敌制胜则推以归功。此马服之代廉颇。而班超之啖郭恂也。以是而尊朱子。其肯欣然享之欤。
曰吾非从王氏也。章次而已。明明违朱子。而曰吾非违朱子也。文义自如。其心不已劳。而其辞不已枝欤。君子之翼圣经距邪说也。理达辞沛。要以明己之道而已。未尝为拙匠而改废绳墨。则彼喙之容与不容。本不足计。况是书也为圣门的传。则入头下手。当以章次为第一义。今既屈而从彼矣。却曰文义则从我。吾见其喙之益长。未见其无所容也。假使真不能容喙。此所谓和岘之乐。非臣之乐也。约束则更之矣。军吏则易置之矣。威敌制胜则推以归功。此马服之代廉颇。而班超之啖郭恂也。以是而尊朱子。其肯欣然享之欤。溪谷曰。中国则学术多歧。我国则挟筴读书者。皆称诵程朱。岂我国士习。果贤于中国耶。曰非然也。中国人才志趣。颇不碌碌。时有有志之士。实心向学。故往往各有实得。我国则不然。龌龊拘束。都无志气。但闻程朱之学世所贵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譬犹垦土播种。有秀有实而后。五谷稊稗可别也。茫然赤地之上。孰为五谷。孰为稊稗哉。溪谷之言。不无意见。其论东人症候。亦未尝不切中膏肓。而细究之则其言亦不免有弊。姑舍程朱。又姑舍当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4H 页
 今。又姑舍我国。试以中国上世孔孟而言之。战国嬴秦之际。天下之学。何尝尽宗孔氏乎。苏张之纵横。申韩之刑名。孙吴之谈兵。圭悝之治赋。学术多歧。奚啻千涂万辙。而其人之志趣不碌碌。岂尽出象山,阳明下哉。汉兴以来。稍尚六经。至董江都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请皆黜之然后。世之挟筴读书者。莫不称诵孔子。其人果皆不龌龊不拘束。才性志气。贤于苏张申韩。与今日我国之诵程朱者。迥然殊科耶。愚亦曰非然也。以其世所贵重。口道而貌尊之者。十居七八耳。然而苏张申韩之时。天下之祸何如。而自汉以降。治化风俗。虽不及三代。人伦粗明。民生粗安。弑父与君。亡失国家之患。比之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犹为稀阔者无他。尊孔氏黜百家之效也。然则拘而就正。犹胜于放而从邪。无益徒乱。又恶用志趣为哉。譬之农焉。无论民之勤惰巧拙。授之谷而教之种。然后粒米握粟。可得而食也。若任其所为。或稊或谷而漫不訾省焉。则及秋而穫。稊谷相半。民犹患饥。毕竟遍地青黄。都是稊稗。一谷不可得见。则其将曰彼青黄者犹贤于赤耶。然则程朱者。今之孔孟也。四
今。又姑舍我国。试以中国上世孔孟而言之。战国嬴秦之际。天下之学。何尝尽宗孔氏乎。苏张之纵横。申韩之刑名。孙吴之谈兵。圭悝之治赋。学术多歧。奚啻千涂万辙。而其人之志趣不碌碌。岂尽出象山,阳明下哉。汉兴以来。稍尚六经。至董江都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请皆黜之然后。世之挟筴读书者。莫不称诵孔子。其人果皆不龌龊不拘束。才性志气。贤于苏张申韩。与今日我国之诵程朱者。迥然殊科耶。愚亦曰非然也。以其世所贵重。口道而貌尊之者。十居七八耳。然而苏张申韩之时。天下之祸何如。而自汉以降。治化风俗。虽不及三代。人伦粗明。民生粗安。弑父与君。亡失国家之患。比之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犹为稀阔者无他。尊孔氏黜百家之效也。然则拘而就正。犹胜于放而从邪。无益徒乱。又恶用志趣为哉。譬之农焉。无论民之勤惰巧拙。授之谷而教之种。然后粒米握粟。可得而食也。若任其所为。或稊或谷而漫不訾省焉。则及秋而穫。稊谷相半。民犹患饥。毕竟遍地青黄。都是稊稗。一谷不可得见。则其将曰彼青黄者犹贤于赤耶。然则程朱者。今之孔孟也。四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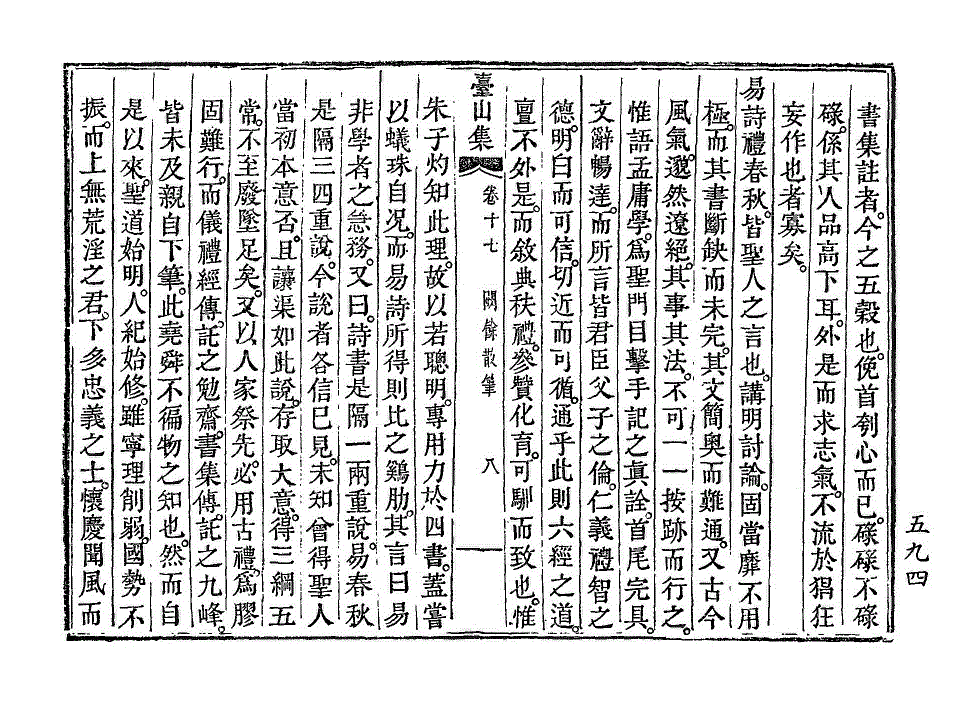 书集注者。今之五谷也。俛首刳心而已。碌碌不碌碌。系其人品高下耳。外是而求志气。不流于猖狂妄作也者寡矣。
书集注者。今之五谷也。俛首刳心而已。碌碌不碌碌。系其人品高下耳。外是而求志气。不流于猖狂妄作也者寡矣。易诗礼春秋。皆圣人之言也。讲明讨论。固当靡不用极。而其书断缺而未完。其文简奥而难通。又古今风气。邈然辽绝。其事其法。不可一一按迹而行之。惟语孟庸学。为圣门目击手记之真诠。首尾完具。文辞畅达。而所言皆君臣父子之伦。仁义礼智之德。明白而可信。切近而可循。通乎此则六经之道。亶不外是。而叙典秩礼。参赞化育。可驯而致也。惟朱子灼知此理。故以若聪明。专用力于四书。盖尝以蚁珠自况。而易诗所得则比之鸡肋。其言曰易非学者之急务。又曰。诗书是隔一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四重说。今说者各信已见。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让渠如此说。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又以人家祭先。必用古礼。为胶固难行。而仪礼经传。托之勉斋。书集传。托之九峰。皆未及亲自下笔。此尧舜不遍物之知也。然而自是以来。圣道始明。人纪始修。虽宁理削弱。国势不振。而上无荒淫之君。下多忠义之士。怀庆闻风而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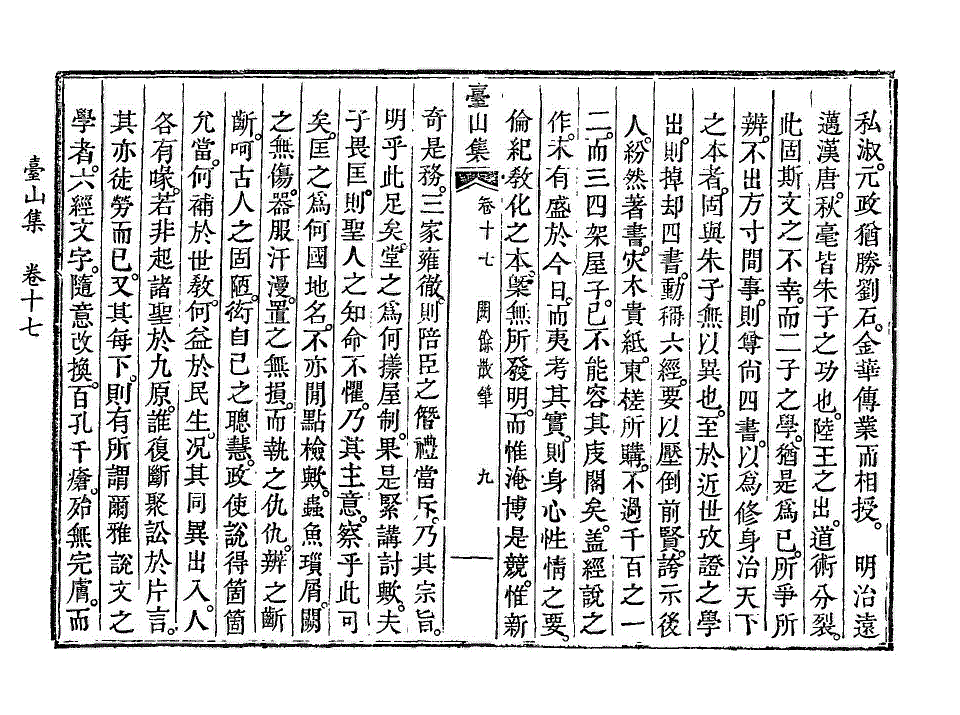 私淑。元政犹胜刘石。金华传业而相授。 明治远迈汉唐。秋毫皆朱子之功也。陆王之出。道术分裂。此固斯文之不幸。而二子之学。犹是为己。所争所辨。不出方寸间事。则尊尚四书。以为修身治天下之本者。固与朱子无以异也。至于近世考證之学出。则掉却四书。动称六经。要以压倒前贤。誇示后人。纷然著书。灾木贵纸。东槎所购。不过千百之一二。而三四架屋子。已不能容其庋阁矣。盖经说之作。未有盛于今日。而夷考其实。则身心性情之要。伦纪教化之本。槩无所发明。而惟淹博是竞。惟新奇是务。三家雍彻。则陪臣之僭礼当斥。乃其宗旨。明乎此足矣。堂之为何㨾屋制。果是紧讲讨欤。夫子畏匡。则圣人之知命不惧。乃其主意。察乎此可矣。匡之为何国地名。不亦閒点检欤。虫鱼琐屑。阙之无伤。器服汗漫。置之无损。而执之仇仇。辨之龂龂。呵古人之固陋。衒自己之聪慧。政使说得个个允当。何补于世教。何益于民生。况其同异出入。人各有喙。若非起诸圣于九原。谁复断聚讼于片言。其亦徒劳而已。又其每下。则有所谓尔雅说文之学者。六经文字。随意改换。百孔千疮。殆无完肤。而
私淑。元政犹胜刘石。金华传业而相授。 明治远迈汉唐。秋毫皆朱子之功也。陆王之出。道术分裂。此固斯文之不幸。而二子之学。犹是为己。所争所辨。不出方寸间事。则尊尚四书。以为修身治天下之本者。固与朱子无以异也。至于近世考證之学出。则掉却四书。动称六经。要以压倒前贤。誇示后人。纷然著书。灾木贵纸。东槎所购。不过千百之一二。而三四架屋子。已不能容其庋阁矣。盖经说之作。未有盛于今日。而夷考其实。则身心性情之要。伦纪教化之本。槩无所发明。而惟淹博是竞。惟新奇是务。三家雍彻。则陪臣之僭礼当斥。乃其宗旨。明乎此足矣。堂之为何㨾屋制。果是紧讲讨欤。夫子畏匡。则圣人之知命不惧。乃其主意。察乎此可矣。匡之为何国地名。不亦閒点检欤。虫鱼琐屑。阙之无伤。器服汗漫。置之无损。而执之仇仇。辨之龂龂。呵古人之固陋。衒自己之聪慧。政使说得个个允当。何补于世教。何益于民生。况其同异出入。人各有喙。若非起诸圣于九原。谁复断聚讼于片言。其亦徒劳而已。又其每下。则有所谓尔雅说文之学者。六经文字。随意改换。百孔千疮。殆无完肤。而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5L 页
 尧舜周孔。举不免岌岌。陆王非不差矣。譬则兄弟分门。各立家计。而事亲奉先。未尝有异论也。今之所谓经学。则骎骎乎矢及黄屋。兵缠紫微。吁亦可畏也哉。
尧舜周孔。举不免岌岌。陆王非不差矣。譬则兄弟分门。各立家计。而事亲奉先。未尝有异论也。今之所谓经学。则骎骎乎矢及黄屋。兵缠紫微。吁亦可畏也哉。我国古之九夷也。幸得箕子东封。称为君子之国。而邃古文献。今不可徵。句济之间。大抵贸贸。崔致远一人。以词藻显于罗季。沿及胜国。稍稍有文士。而极其所长。不过骈俪律绝。摹唐轨宋而止耳。自序记古文辞以往。已无一篇可称道者。况向上儒者事业。宜乎其未有闻也。圃隐以间世英豪。当 有明作兴之会。朱子编著诸书。又适次第东来。遂得以探讨服行。杰然为从周用夏之祖。而 熙朝继之。渊源统绪。始烂焉可述。盖夷荒之渐被声教。若是其难也。然而 国初风气。犹近大朴。文质未兼。醇疵相半。阳村之柔懦。毕斋之强厉。皆不免一偏之病。而著述之行于世者。脱不得艺苑习气。寒暄笃于持守。静庵奋于经济。皆未及立言垂后。惟退溪功深真积。栗谷姿邻殆庶。华阳之刚大。三洲之明允。卓为儒宗。并有论著。而宪章祖述。悉本紫阳。今以诸先生文集与中国群儒所著。对举而参看。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6H 页
 则典籍之未广而腹笥或逊淹洽。方俚之转译而舌锋或欠铦利。则诚亦往往有之。而此不过枝叶细瑕耳。若其大经大法。固可以考不谬俟不惑。而南轩之失于疏快。东莱之伤于纤巧。亦或姑舍而非所愿也。况儒之为业。自有本领。言语文字。乃其馀事。诸先生皆有孝弟至行。忠贞大节。致主泽民之烈。出处进退之风。本末具备。终始无疵。虽进而置之庆历,元祐之际。恐不必多让人先。居是邦而读其书者。固当没身山仰。不敢有一毫侮慢之意也。前辈既远。遗泽浸微。簪缨骄子。裙屐恶少。幼不知洒扫之事。长不操书筴之业。金银杖杜。荡无顾忌。一脉儒种。固已无地可植。而间有稍挟辩慧。临深自高者。欲染指文学。为哗世沽誉之计。则无奈程朱典训。象魏俨临。性味相反。肌肤如伤。又厌又恶。要破不得。于斯时也。燕肆唐板。滚滚东出。伪讹之撰。逾后逾博。巧曲之解。逾新逾奇。则八公草木。盖已望风心折。而诋斥程朱。则麻姑之搔背也。推尊郑孔。则水母之借目也。乃敢肆然而号于众曰。汉唐先于有宋。六经高于四子。城朝兔园。卑卑休论。于是乎朱子许多年刿心鉥目。为前圣为后学。
则典籍之未广而腹笥或逊淹洽。方俚之转译而舌锋或欠铦利。则诚亦往往有之。而此不过枝叶细瑕耳。若其大经大法。固可以考不谬俟不惑。而南轩之失于疏快。东莱之伤于纤巧。亦或姑舍而非所愿也。况儒之为业。自有本领。言语文字。乃其馀事。诸先生皆有孝弟至行。忠贞大节。致主泽民之烈。出处进退之风。本末具备。终始无疵。虽进而置之庆历,元祐之际。恐不必多让人先。居是邦而读其书者。固当没身山仰。不敢有一毫侮慢之意也。前辈既远。遗泽浸微。簪缨骄子。裙屐恶少。幼不知洒扫之事。长不操书筴之业。金银杖杜。荡无顾忌。一脉儒种。固已无地可植。而间有稍挟辩慧。临深自高者。欲染指文学。为哗世沽誉之计。则无奈程朱典训。象魏俨临。性味相反。肌肤如伤。又厌又恶。要破不得。于斯时也。燕肆唐板。滚滚东出。伪讹之撰。逾后逾博。巧曲之解。逾新逾奇。则八公草木。盖已望风心折。而诋斥程朱。则麻姑之搔背也。推尊郑孔。则水母之借目也。乃敢肆然而号于众曰。汉唐先于有宋。六经高于四子。城朝兔园。卑卑休论。于是乎朱子许多年刿心鉥目。为前圣为后学。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6L 页
 积费纸墨者。不待火而已索然煨烬矣。朱子既然。则诸贤之出于蓝水者。有一人得免为田舍翁者乎。王莽狭小汉制。安石卑薄仁皇。其言甚侈。似可以诳耀一时。而未知终竟优劣果如何耳。
积费纸墨者。不待火而已索然煨烬矣。朱子既然。则诸贤之出于蓝水者。有一人得免为田舍翁者乎。王莽狭小汉制。安石卑薄仁皇。其言甚侈。似可以诳耀一时。而未知终竟优劣果如何耳。叶水心曰。国无骏功。良法先亡。士无骏材。良心先丧。此切至之言而悲痛之辞也。然良法之亡。一日修之而有馀。良心之丧。百年养之而不足。今日良心之丧。盖亦极矣。若非圣君贤辅明正学斥邪说。躬行心得。表率于上。而教化风尚。以复其本性之好恶。荣辱赏罚。以导其常情之趋避。奋之以投袂之勇。行之以徙木之信。持之以移山之久。则汤汤洪水。吾不知其攸济矣。
我先王正庙圣人也。以聪明首出之姿。有忧戚玉成之工。自在春邸。令闻夙畅。作其即位。四方拭目。惇典庸礼。祖述姚姒。右贤左戚。跨越汉唐。万几之暇。课读如诸生。以一部朱书。为作人化俗之本。每叹世级渐下。士趋不端。学务新奇。文尚尖巧。恩诲威董。屡形丝纶。尝临轩策士。历论 明清以来学术之弊。丰坊孙矿之非圣诬经。杨慎季本之曲说凿解。七子五子之裨贩剽窃。无不洞叙源委。严加辟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7H 页
 廓。又命燕行往来。勿购新书。犯者抵罪。盖 圣学高明。大本既立。又于近世中州书籍。阅览靡遗。灼知其无益有害。而既不得抚临华夏。身任大一统之治。则姑欲遏其滋蔓。捍其横流。使我左海一区。得免稂莠之乱垫溺之患也。非圣人而能如是乎。御制弘斋全书二百馀卷。实为义理渊海。政宜播之域中。家习人诵。而升遐后十馀年。始得编印。以数十件。分藏内外馆阁五处史库而已。臣叨守江都。谨取外阁所藏。伏而读之。尽数月乃已。俯仰愀忾。益不禁朱弦绿竹之思。
廓。又命燕行往来。勿购新书。犯者抵罪。盖 圣学高明。大本既立。又于近世中州书籍。阅览靡遗。灼知其无益有害。而既不得抚临华夏。身任大一统之治。则姑欲遏其滋蔓。捍其横流。使我左海一区。得免稂莠之乱垫溺之患也。非圣人而能如是乎。御制弘斋全书二百馀卷。实为义理渊海。政宜播之域中。家习人诵。而升遐后十馀年。始得编印。以数十件。分藏内外馆阁五处史库而已。臣叨守江都。谨取外阁所藏。伏而读之。尽数月乃已。俯仰愀忾。益不禁朱弦绿竹之思。阮葵生。乾隆间人。所著茶馀客话。载其伯祖樾轩(应商)戒子弟语。曰近见后生小子。皆喜读毛西河集。其称引未足为据。必须搜讨源头。字字质證。慎勿为悬河之口所谩。又记阎百诗话。曰汪尧峰(琬)私造典礼。李天生(因笃)杜撰故实。毛大可(奇龄)割裂经文。贻误后学匪浅。汪李毛三人。皆清初钜儒。近日东士所津津艳慕。以为地负海涵者也。而中州则相去未远。已有觑破伎俩。而不为其所瞒者。此东人之不及中州处也。
见行十三经。尔雅居其一。释诂一篇。传以为周公所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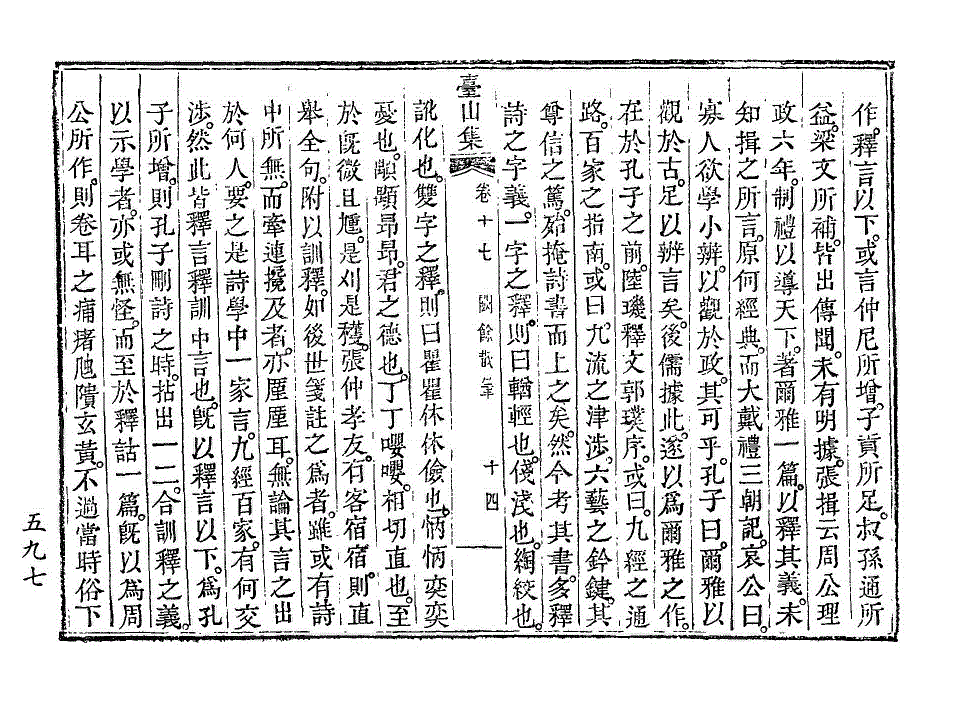 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贡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皆出传闻。未有明据。张揖云周公理政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未知揖之所言。原何经典。而大戴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后儒据此。遂以为尔雅之作。在于孔子之前。陆玑释文郭璞序。或曰。九经之通路。百家之指南。或曰。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其尊信之笃。殆掩诗书而上之矣。然今考其书。多释诗之字义。一字之释。则曰輶轻也。俴浅也。绹绞也。讹化也。双字之释。则曰瞿瞿休休俭也。怲怲奕奕忧也。颙颙昂昂。君之德也。丁丁嘤嘤。相切直也。至于既微且尰。是刈是穫。张仲孝友。有客宿宿。则直举全句。附以训释。如后世笺注之为者。虽或有诗中所无。而牵连搀及者。亦廑廑耳。无论其言之出于何人。要之是诗学中一家言。九经百家。有何交涉。然此皆释言释训中言也。既以释言以下。为孔子所增。则孔子删诗之时。拈出一二。合训释之义。以示学者。亦或无怪。而至于释诂一篇。既以为周公所作。则卷耳之痡瘏虺隤玄黄。不过当时俗下
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贡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皆出传闻。未有明据。张揖云周公理政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未知揖之所言。原何经典。而大戴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后儒据此。遂以为尔雅之作。在于孔子之前。陆玑释文郭璞序。或曰。九经之通路。百家之指南。或曰。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其尊信之笃。殆掩诗书而上之矣。然今考其书。多释诗之字义。一字之释。则曰輶轻也。俴浅也。绹绞也。讹化也。双字之释。则曰瞿瞿休休俭也。怲怲奕奕忧也。颙颙昂昂。君之德也。丁丁嘤嘤。相切直也。至于既微且尰。是刈是穫。张仲孝友。有客宿宿。则直举全句。附以训释。如后世笺注之为者。虽或有诗中所无。而牵连搀及者。亦廑廑耳。无论其言之出于何人。要之是诗学中一家言。九经百家。有何交涉。然此皆释言释训中言也。既以释言以下。为孔子所增。则孔子删诗之时。拈出一二。合训释之义。以示学者。亦或无怪。而至于释诂一篇。既以为周公所作。则卷耳之痡瘏虺隤玄黄。不过当时俗下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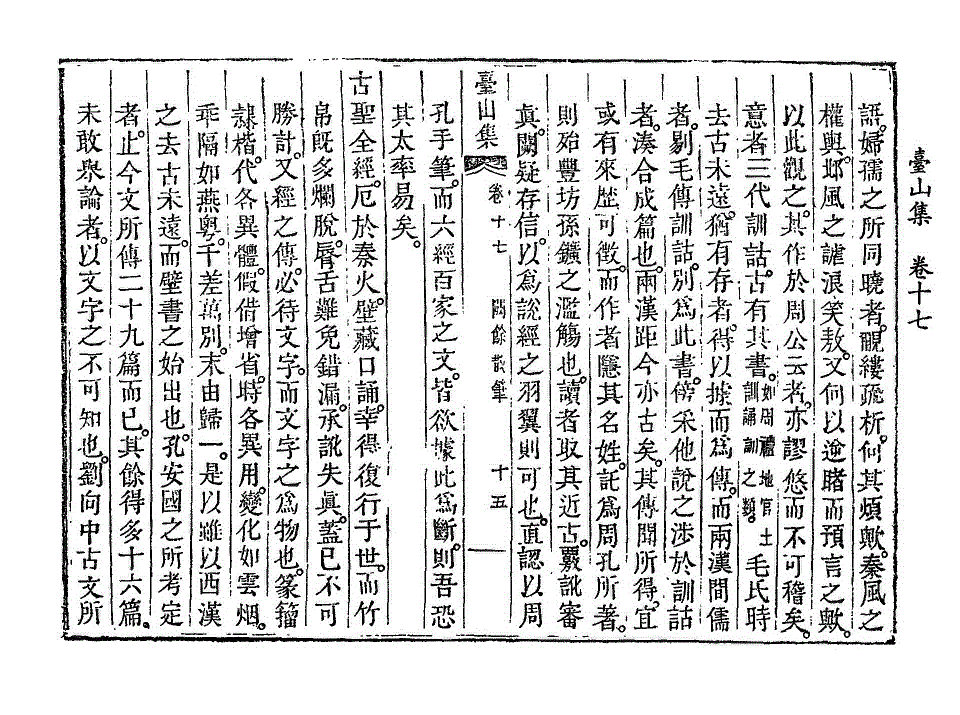 语。妇孺之所同晓者。覼缕疏析。何其烦欤。秦风之权舆。邶风之谑浪笑敖。又何以逆睹而预言之欤。以此观之。其作于周公云者。亦谬悠而不可稽矣。意者三代训诂。古有其书。(如周礼地官土训诵训之类。)毛氏时去古未远。犹有存者。得以据而为传。而两汉间儒者。剔毛传训诂。别为此书。傍采他说之涉于训诂者。凑合成篇也。两汉距今亦古矣。其传闻所得。宜或有来历可徵。而作者隐其名姓。托为周孔所著。则殆丰坊孙矿之滥觞也。读者取其近古。覈讹审真。阙疑存信。以为说经之羽翼则可也。直认以周孔手笔。而六经百家之文。皆欲据此为断。则吾恐其太率易矣。
语。妇孺之所同晓者。覼缕疏析。何其烦欤。秦风之权舆。邶风之谑浪笑敖。又何以逆睹而预言之欤。以此观之。其作于周公云者。亦谬悠而不可稽矣。意者三代训诂。古有其书。(如周礼地官土训诵训之类。)毛氏时去古未远。犹有存者。得以据而为传。而两汉间儒者。剔毛传训诂。别为此书。傍采他说之涉于训诂者。凑合成篇也。两汉距今亦古矣。其传闻所得。宜或有来历可徵。而作者隐其名姓。托为周孔所著。则殆丰坊孙矿之滥觞也。读者取其近古。覈讹审真。阙疑存信。以为说经之羽翼则可也。直认以周孔手笔。而六经百家之文。皆欲据此为断。则吾恐其太率易矣。古圣全经。厄于秦火。壁藏口诵。幸得复行于世。而竹帛既多烂脱。唇舌难免错漏。承讹失真。盖已不可胜计。又经之传。必待文字。而文字之为物也。篆籀隶楷。代各异体。假借增省。时各异用。变化如云烟。乖隔如燕粤。千差万别。末由归一。是以虽以西汉之去古未远。而壁书之始出也。孔安国之所考定者。止今文所传二十九篇而已。其馀得多十六篇。未敢举论者。以文字之不可知也。刘向中古文所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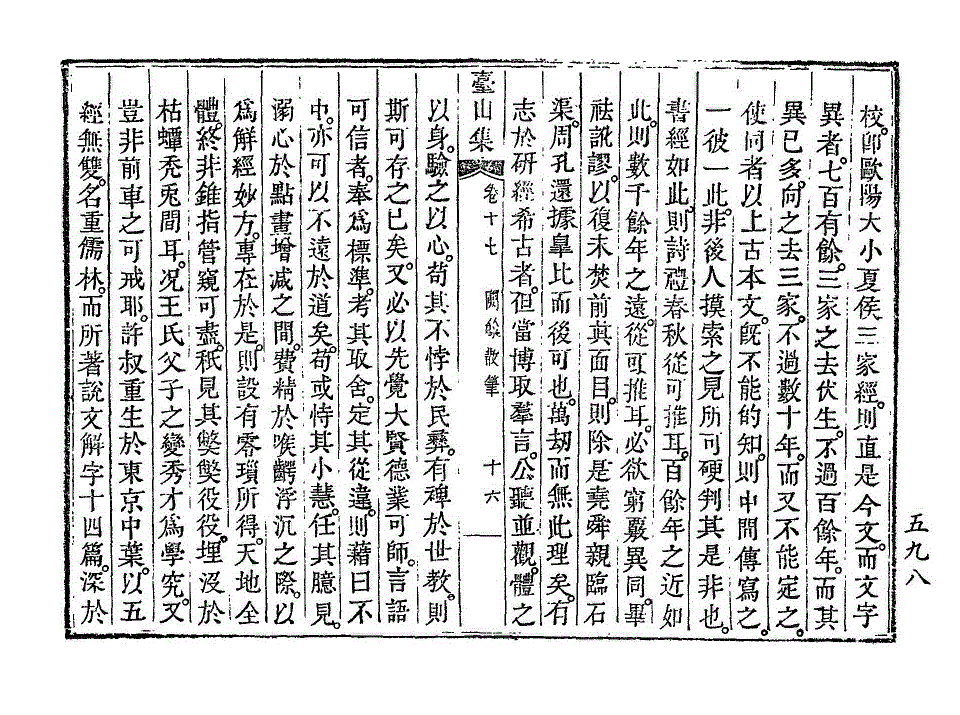 校。即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则直是今文。而文字异者。七百有馀。三家之去伏生。不过百馀年。而其异已多。向之去三家。不过数十年。而又不能定之。使同者以上古本文。既不能的知。则中间传写之。一彼一此。非后人摸索之见所可硬判其是非也。书经如此。则诗礼春秋从可推耳。百馀年之近如此。则数千馀年之远。从可推耳。必欲穷覈异同。毕祛讹谬。以复未焚前真面目。则除是尧舜亲临石渠。周孔还据皋比而后可也。万劫而无此理矣。有志于研经希古者。但当博取群言。公听并观。体之以身。验之以心。苟其不悖于民彝。有裨于世教。则斯可存之已矣。又必以先觉大贤德业可师。言语可信者。奉为标准。考其取舍。定其从违。则藉曰不中。亦可以不远于道矣。苟或恃其小慧。任其臆见。溺心于点画增减之间。费精于喉腭浮沉之际。以为解经妙方。专在于是。则设有零琐所得。天地全体。终非锥指管窥可尽。秖见其弊弊役役。埋没于枯蟫秃兔间耳。况王氏父子之变秀才为学究。又岂非前车之可戒耶。许叔重生于东京中叶。以五经无双。名重儒林。而所著说文解字十四篇。深于
校。即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则直是今文。而文字异者。七百有馀。三家之去伏生。不过百馀年。而其异已多。向之去三家。不过数十年。而又不能定之。使同者以上古本文。既不能的知。则中间传写之。一彼一此。非后人摸索之见所可硬判其是非也。书经如此。则诗礼春秋从可推耳。百馀年之近如此。则数千馀年之远。从可推耳。必欲穷覈异同。毕祛讹谬。以复未焚前真面目。则除是尧舜亲临石渠。周孔还据皋比而后可也。万劫而无此理矣。有志于研经希古者。但当博取群言。公听并观。体之以身。验之以心。苟其不悖于民彝。有裨于世教。则斯可存之已矣。又必以先觉大贤德业可师。言语可信者。奉为标准。考其取舍。定其从违。则藉曰不中。亦可以不远于道矣。苟或恃其小慧。任其臆见。溺心于点画增减之间。费精于喉腭浮沉之际。以为解经妙方。专在于是。则设有零琐所得。天地全体。终非锥指管窥可尽。秖见其弊弊役役。埋没于枯蟫秃兔间耳。况王氏父子之变秀才为学究。又岂非前车之可戒耶。许叔重生于东京中叶。以五经无双。名重儒林。而所著说文解字十四篇。深于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9H 页
 六书之义。勘究声形。援證经典。尽多精密可喜。其裨补斯文之功。固不下于康成诸贤。而是特据当时文字可考者而推测为说耳。至若孔壁以前上世科斗。孔安国之所不能知。刘子政之所不能校。则吾恐叔重亦末如之何矣。然则虽使今之经籍。一一刊改。以从许氏。是不过为许氏之经而止耳。未知尧舜周孔真面目之载在科斗原本者。皆果一一准此。无毫发馀憾否。
六书之义。勘究声形。援證经典。尽多精密可喜。其裨补斯文之功。固不下于康成诸贤。而是特据当时文字可考者而推测为说耳。至若孔壁以前上世科斗。孔安国之所不能知。刘子政之所不能校。则吾恐叔重亦末如之何矣。然则虽使今之经籍。一一刊改。以从许氏。是不过为许氏之经而止耳。未知尧舜周孔真面目之载在科斗原本者。皆果一一准此。无毫发馀憾否。郑康成尝驳许慎五经异义。颜氏家训云说文中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顾亭林亦论其支离穿凿数十条。今见日知录。
中庸仁者人也。郑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孔疏曰。仁谓仁恩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已亲。朱子与吕东莱书曰。中庸注相人偶。不知出于何书。所谓人意相存问者。却似说得字义。有意思也。窃详相人偶者。汉时行用俗语。盖与人相接亲爱之意。故郑氏注诸经。凡两人相接处。辄用此语。如大射仪揖以偶注。以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人偶也。聘礼每曲揖注。以人相人偶为敬也。公食大夫礼宾入
台山集卷十七 第 599L 页
 相揖注。相人偶。论语管仲人也注。人偶同位之辞。诗匪风笺。人偶能烹鱼。人偶能辅周道治民之类是已。然礼注诗笺。文既太略。义亦少迂。未甚可信。而中庸注则较之他处。颇详备衬切。盖仁之为字。本以爱人而名。仁者人也。提示仁字得名之由。而下文亲亲为大。言爱人之中。亲亲为最大也。相人偶。即俗语爱人之称。而在当时人所易晓。故举以證明。殊觉有味。朱子所谓说得字义有意思者以此也。然章句不用此说。而改以他训者。此三字辞意艰晦。朱子意其或出于古书而考之未得。故慎于承用。而今训人身生理之说。于人字义。亦可通也。然以亲对人。远近相形。与有子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亲亲仁民等说。互相发明。则郑注之弃。终似可惜。
相揖注。相人偶。论语管仲人也注。人偶同位之辞。诗匪风笺。人偶能烹鱼。人偶能辅周道治民之类是已。然礼注诗笺。文既太略。义亦少迂。未甚可信。而中庸注则较之他处。颇详备衬切。盖仁之为字。本以爱人而名。仁者人也。提示仁字得名之由。而下文亲亲为大。言爱人之中。亲亲为最大也。相人偶。即俗语爱人之称。而在当时人所易晓。故举以證明。殊觉有味。朱子所谓说得字义有意思者以此也。然章句不用此说。而改以他训者。此三字辞意艰晦。朱子意其或出于古书而考之未得。故慎于承用。而今训人身生理之说。于人字义。亦可通也。然以亲对人。远近相形。与有子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亲亲仁民等说。互相发明。则郑注之弃。终似可惜。相人偶三字。于仁字爱人之本义。虽似衬切。而此指仁之发用处而言耳。若无此心之德为其体干。则彼发用者何从而生乎。既有此体干。则又将何字而名之乎。譬之木焉。根枝皆木。譬之水焉。源流皆水。若曰木之为字。可称于枝。不可称于根。水之为字。可称于流。不可称于源。此坚白风幡之说也。圣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0H 页
 人论仁。不一其旨。或体或用。言各有当。章句集注之为训也。一从本旨所在。于其发用处则曰利泽。及人曰教化浃。未尝不以爱人言之。而于其体干处。则曰爱之理心之德。曰本心全德。曰当理而无私心。其为说。虽若参差不齐。而彼此互发。本末兼举。仁之为物。焕然可睹。而要其功效。总不出亲人爱人之事。汉唐注家。无能臻此。而释氏空虚之见。虽欲强觅而求其似。不可得也。近见清学士阮元所著论孟论仁论。专据相人偶三字。以蔽许多言仁。其言曰。许叔重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即人偶之意。圣贤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见。孔子之仁待老少。始见安怀。若心无所着。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便可毕仁之事。又曰。孟子虽以恻隐为仁。乃仁之端。非仁之实。必扩而充之。著于事实。始可称仁。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其意专在于诋毁集注。而名以论学。言之无理。乃至此乎。千言万语。从他扰扰。有一句话可以解惑者。凡言始可见者。据人目所及而言耳。非物之本无忽有之谓也。譬如人在室中不可见。待出户而始可见。若室中本无此人。则出户可见者。竟
人论仁。不一其旨。或体或用。言各有当。章句集注之为训也。一从本旨所在。于其发用处则曰利泽。及人曰教化浃。未尝不以爱人言之。而于其体干处。则曰爱之理心之德。曰本心全德。曰当理而无私心。其为说。虽若参差不齐。而彼此互发。本末兼举。仁之为物。焕然可睹。而要其功效。总不出亲人爱人之事。汉唐注家。无能臻此。而释氏空虚之见。虽欲强觅而求其似。不可得也。近见清学士阮元所著论孟论仁论。专据相人偶三字。以蔽许多言仁。其言曰。许叔重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即人偶之意。圣贤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见。孔子之仁待老少。始见安怀。若心无所着。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便可毕仁之事。又曰。孟子虽以恻隐为仁。乃仁之端。非仁之实。必扩而充之。著于事实。始可称仁。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其意专在于诋毁集注。而名以论学。言之无理。乃至此乎。千言万语。从他扰扰。有一句话可以解惑者。凡言始可见者。据人目所及而言耳。非物之本无忽有之谓也。譬如人在室中不可见。待出户而始可见。若室中本无此人。则出户可见者。竟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0L 页
 是何物。若谓出户可见者。方可称人。则在室不可见者。不得称人乎。一矛一盾。即地破绽。自然之理。终非辩说所能文也。且夫所恶于释氏慈悲者。以其背亲畔看。灭绝人类。名虽慈悲。实则相戾也。若单说慈悲。则慈悲何罪。圣人之全此本心。满腔恻隐。虽谓之一片慈悲。固无不可。而亲亲仁民。恩及四海。老僧面壁。何尝有此。不察其实之绝不同。而欲讳其形之略相似。是何异于恶紫而废朱。惩莠而去苗乎。若曰恩及四海。初无待于满腔恻隐。则是食谷而忘其种。生子而秘其胎也。恶乎可也。至若仁端非仁云云。即上所谓根源非水木之说也。玆不复辨。
是何物。若谓出户可见者。方可称人。则在室不可见者。不得称人乎。一矛一盾。即地破绽。自然之理。终非辩说所能文也。且夫所恶于释氏慈悲者。以其背亲畔看。灭绝人类。名虽慈悲。实则相戾也。若单说慈悲。则慈悲何罪。圣人之全此本心。满腔恻隐。虽谓之一片慈悲。固无不可。而亲亲仁民。恩及四海。老僧面壁。何尝有此。不察其实之绝不同。而欲讳其形之略相似。是何异于恶紫而废朱。惩莠而去苗乎。若曰恩及四海。初无待于满腔恻隐。则是食谷而忘其种。生子而秘其胎也。恶乎可也。至若仁端非仁云云。即上所谓根源非水木之说也。玆不复辨。中庸天命之谓性。郑注曰。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朱子与吕东莱书曰。中庸古注。极有好处。如说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后来杂佛老而言者。岂能如是悫实耶。其尊尚也至矣。郑氏所谓木神则仁者。指性而言耳。使阮氏释此仁字。将以为仁之端耶。将以为仁之事耶。以为事也。则性中未有事物。相人偶三字。恐着不得。以为端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1H 页
 也。则端非仁之实。何得直称为仁耶。(端者发见之称。而阮说曰。具心者仁之端也。亦是错解。而姑依其说辨之。)近日学者。动称汉儒。所积憾于朱子者。以其不纯用古注。而开卷第一义。朱子之所尊尚者。却又掉头不讲。毕竟其学。非宋非汉。只是自己之私见。实事求是者。果如是乎。
也。则端非仁之实。何得直称为仁耶。(端者发见之称。而阮说曰。具心者仁之端也。亦是错解。而姑依其说辨之。)近日学者。动称汉儒。所积憾于朱子者。以其不纯用古注。而开卷第一义。朱子之所尊尚者。却又掉头不讲。毕竟其学。非宋非汉。只是自己之私见。实事求是者。果如是乎。阮集。有性命古训一篇。盖为斥李翱复性书而作也。采集诗书礼孝经春秋论孟言性命之说。而逐段以已意附论。总断之曰。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故实而易于率循。晋唐人言性命多在心。故虚而易于傅会。儒释之分。在于此。又曰。孔子教颜渊。惟闻复礼。未闻复性。又力主孟子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命也一段。及礼记性之欲一句。以为欲在性之内。不可绝。绝欲者佛教也。按李翱之书曰。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为也。情者。妄也邪也。情之动静不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寂然不动。邪思自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翱之以明言性。以觉言复。固杂佛老而言者也。前人之辨。辟已备矣。(朱子曰。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此乃释氏之说。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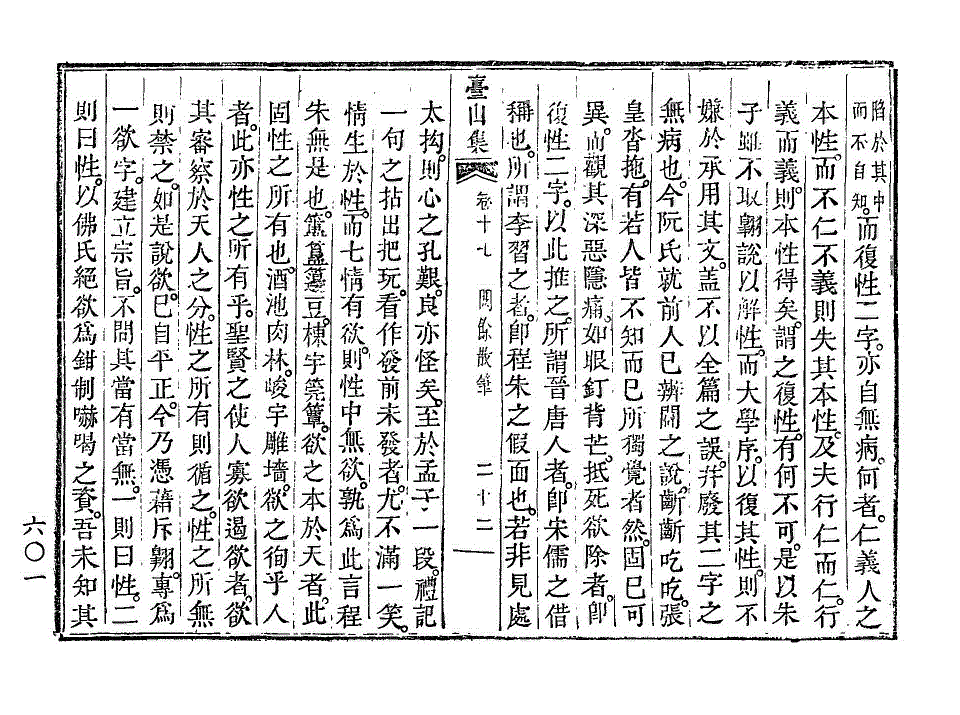 陷于其中而不自知。)而复性二字。亦自无病。何者。仁义人之本性。而不仁不义则失其本性。及夫行仁而仁。行义而义。则本性得矣。谓之复性。有何不可。是以朱子虽不取翱说以解性。而大学序。以复其性。则不嫌于承用其文。盖不以全篇之误。并废其二字之无病也。今阮氏就前人已辨辟之说。龂龂吃吃。张皇沓拖。有若人皆不知而已所独觉者然。固已可异。而观其深恶隐痛。如眼钉背芒。抵死欲除者。即复性二字。以此推之。所谓晋唐人者。即宋儒之借称也。所谓李习之者。即程朱之假面也。若非见处太拘。则心之孔艰。良亦怪矣。至于孟子一段。礼记一句之拈出把玩。看作发前未发者。尤不满一笑。情生于性。而七情有欲。则性中无欲。孰为此言程朱无是也。簠簋笾豆。栋宇筦簟。欲之本于天者。此固性之所有也。酒池肉林。峻宇雕墙。欲之徇乎人者。此亦性之所有乎。圣贤之使人寡欲遏欲者。欲其审察于天人之分。性之所有则循之。性之所无则禁之。如是说欲。已自平正。今乃凭藉斥翱。专为一欲字。建立宗旨。不问其当有当无。一则曰性。二则曰性。以佛氏绝欲为钳制吓喝之资。吾未知其
陷于其中而不自知。)而复性二字。亦自无病。何者。仁义人之本性。而不仁不义则失其本性。及夫行仁而仁。行义而义。则本性得矣。谓之复性。有何不可。是以朱子虽不取翱说以解性。而大学序。以复其性。则不嫌于承用其文。盖不以全篇之误。并废其二字之无病也。今阮氏就前人已辨辟之说。龂龂吃吃。张皇沓拖。有若人皆不知而已所独觉者然。固已可异。而观其深恶隐痛。如眼钉背芒。抵死欲除者。即复性二字。以此推之。所谓晋唐人者。即宋儒之借称也。所谓李习之者。即程朱之假面也。若非见处太拘。则心之孔艰。良亦怪矣。至于孟子一段。礼记一句之拈出把玩。看作发前未发者。尤不满一笑。情生于性。而七情有欲。则性中无欲。孰为此言程朱无是也。簠簋笾豆。栋宇筦簟。欲之本于天者。此固性之所有也。酒池肉林。峻宇雕墙。欲之徇乎人者。此亦性之所有乎。圣贤之使人寡欲遏欲者。欲其审察于天人之分。性之所有则循之。性之所无则禁之。如是说欲。已自平正。今乃凭藉斥翱。专为一欲字。建立宗旨。不问其当有当无。一则曰性。二则曰性。以佛氏绝欲为钳制吓喝之资。吾未知其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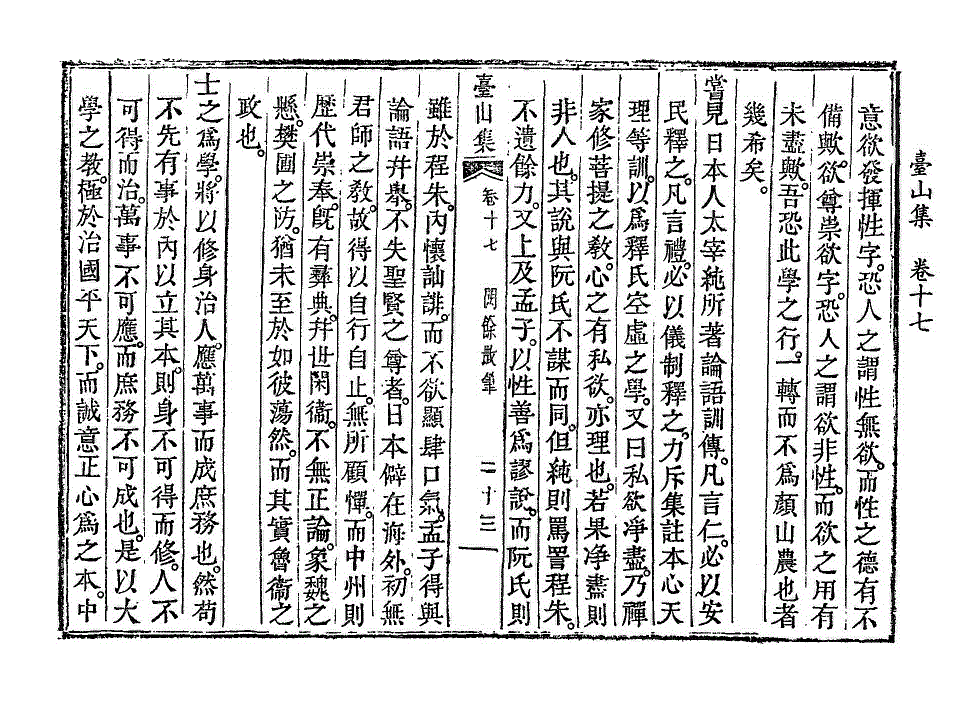 意欲发挥性字。恐人之谓性无欲。而性之德有不备欤。欲尊崇欲字。恐人之谓欲非性。而欲之用有未尽欤。吾恐此学之行。一转而不为颜山农也者几希矣。
意欲发挥性字。恐人之谓性无欲。而性之德有不备欤。欲尊崇欲字。恐人之谓欲非性。而欲之用有未尽欤。吾恐此学之行。一转而不为颜山农也者几希矣。尝见日本人太宰纯所著论语训传。凡言仁。必以安民释之。凡言礼。必以仪制释之。力斥集注本心天理等训。以为释氏空虚之学。又曰私欲净尽。乃禅家修菩提之教。心之有私欲。亦理也。若果净尽则非人也。其说与阮氏不谋而同。但纯则骂詈程朱。不遗馀力。又上及孟子。以性善为谬说。而阮氏则虽于程朱。内怀讪诽。而不欲显肆口气。孟子得与论语并举。不失圣贤之尊者。日本僻在海外。初无君师之教。故得以自行自止。无所顾惮。而中州则历代崇奉。既有彝典。并世闲卫。不无正论。象魏之悬。樊圃之防。犹未至于如彼荡然。而其实鲁卫之政也。
士之为学。将以修身治人。应万事而成庶务也。然苟不先有事于内以立其本。则身不可得而修。人不可得而治。万事不可应。而庶务不可成也。是以大学之教。极于治国平天下。而诚意正心为之本。中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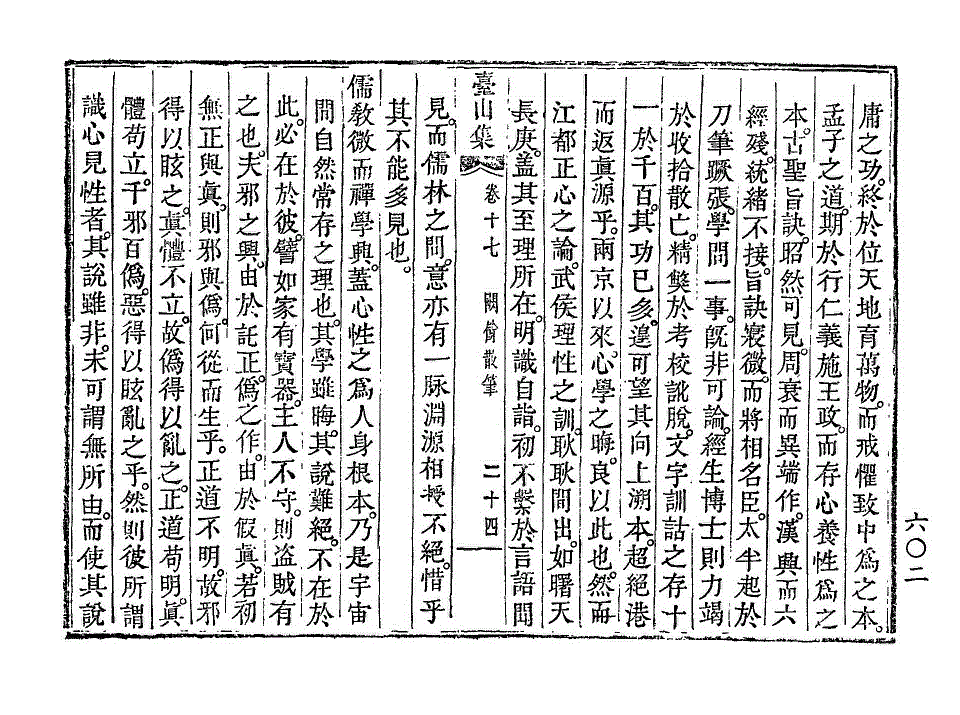 庸之功。终于位天地育万物。而戒惧致中为之本。孟子之道。期于行仁义施王政。而存心养性为之本。古圣旨诀。昭然可见。周衰而异端作。汉兴而六经残。统绪不接。旨诀寝微。而将相名臣。太半起于刀笔蹶张。学问一事。既非可论。经生博士则力竭于收拾散亡。精弊于考校讹脱。文字训诂之存十一于千百。其功已多。遑可望其向上溯本。超绝港而返真源乎。两京以来。心学之晦。良以此也。然而江都正心之论。武侯理性之训。耿耿间出。如曙天长庚。盖其至理所在。明识自诣。初不系于言语闻见。而儒林之间。意亦有一脉渊源相授不绝。惜乎其不能多见也。
庸之功。终于位天地育万物。而戒惧致中为之本。孟子之道。期于行仁义施王政。而存心养性为之本。古圣旨诀。昭然可见。周衰而异端作。汉兴而六经残。统绪不接。旨诀寝微。而将相名臣。太半起于刀笔蹶张。学问一事。既非可论。经生博士则力竭于收拾散亡。精弊于考校讹脱。文字训诂之存十一于千百。其功已多。遑可望其向上溯本。超绝港而返真源乎。两京以来。心学之晦。良以此也。然而江都正心之论。武侯理性之训。耿耿间出。如曙天长庚。盖其至理所在。明识自诣。初不系于言语闻见。而儒林之间。意亦有一脉渊源相授不绝。惜乎其不能多见也。儒教微而禅学兴。盖心性之为人身根本。乃是宇宙间自然常存之理也。其学虽晦。其说难绝。不在于此。必在于彼。譬如家有宝器。主人不守。则盗贼有之也。夫邪之兴。由于托正。伪之作。由于假真。若初无正与真。则邪与伪。何从而生乎。正道不明。故邪得以眩之。真体不立。故伪得以乱之。正道苟明。真体苟立。千邪百伪。恶得以眩乱之乎。然则彼所谓识心见性者。其说虽非。未可谓无所由。而使其说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3H 页
 猖狂自肆。得售眩乱。则亦两汉诸儒不讲心性之过也。仁义不行而杨墨托焉。其差也至于无父无君。无父无君可诛也。仁义之道。不可废也。心性不讲而禅释托焉。其弊也至于空虚寂灭。空虚寂灭可斥也。心性之说。不可绝也。今恶禅释而讳言心性。何异于恶杨墨而讳言仁义乎。
猖狂自肆。得售眩乱。则亦两汉诸儒不讲心性之过也。仁义不行而杨墨托焉。其差也至于无父无君。无父无君可诛也。仁义之道。不可废也。心性不讲而禅释托焉。其弊也至于空虚寂灭。空虚寂灭可斥也。心性之说。不可绝也。今恶禅释而讳言心性。何异于恶杨墨而讳言仁义乎。二程朱子。生于绝学之后。洞见大道之原。揭此真正。折彼邪伪题目。则不嫌其同。而指趣之殊。实相燕越。知心为一身之本。而中无主则本不固。故曰居敬以立其本。知心具万物之知。而理不穷则知有蔽。故曰穷理以致其知。凡所谓居敬穷理。立本致知者。将以率五常之性。行五伦之道。修身治人。应万事而成庶务也。故曰力行以践其实。其为说也。真实有据。其为学也。中正无弊。禅释空虚邪伪之见。其果有一毫近似者乎。
韩子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孔子之说。长于周公。孟子之说。长于孔子。位愈卑世愈降。而其说愈长。理势然也。况朱子之位与世。比之孔孟。又甚辽绝。而所自任以明道垂教者。非注解则问答。言语之多。夫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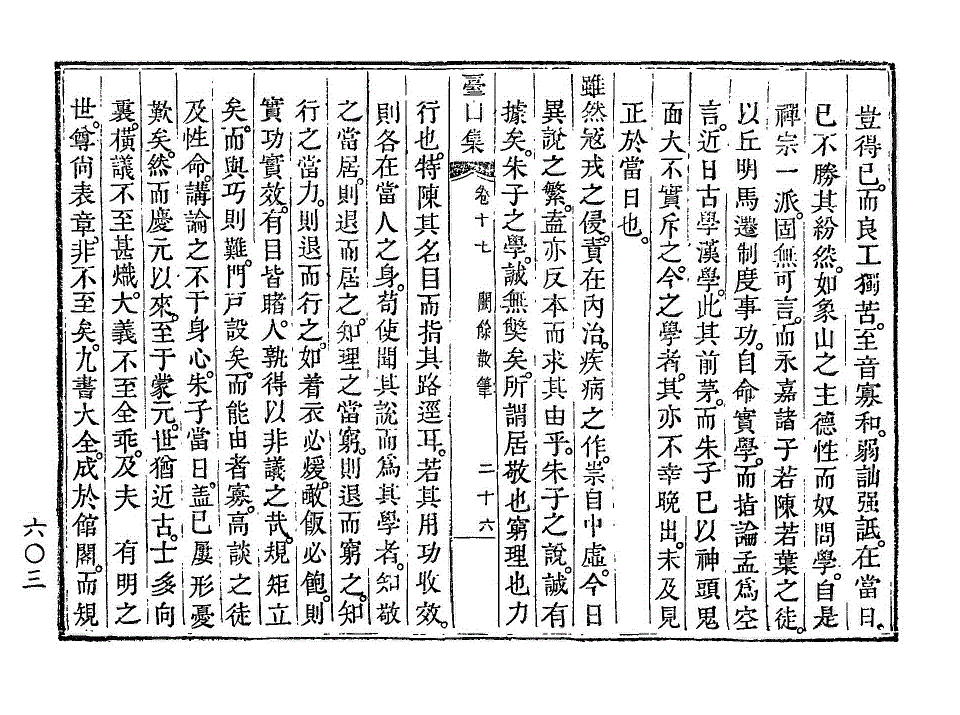 岂得已。而良工独苦。至音寡和。弱讪强诋。在当日。已不胜其纷然。如象山之主德性而奴问学。自是禅宗一派。固无可言。而永嘉诸子若陈若叶之徒。以丘明马迁制度事功。自命实学。而指论孟为空言。近日古学汉学。此其前茅。而朱子已以神头鬼面大不实斥之。今之学者。其亦不幸晚出。未及见正于当日也。
岂得已。而良工独苦。至音寡和。弱讪强诋。在当日。已不胜其纷然。如象山之主德性而奴问学。自是禅宗一派。固无可言。而永嘉诸子若陈若叶之徒。以丘明马迁制度事功。自命实学。而指论孟为空言。近日古学汉学。此其前茅。而朱子已以神头鬼面大不实斥之。今之学者。其亦不幸晚出。未及见正于当日也。虽然寇戎之侵。责在内治。疾病之作。崇自中虚。今日异说之繁。盍亦反本而求其由乎。朱子之说。诚有据矣。朱子之学。诚无弊矣。所谓居敬也穷理也力行也。特陈其名目而指其路径耳。若其用功收效。则各在当人之身。苟使闻其说而为其学者。知敬之当居。则退而居之。知理之当穷。则退而穷之。知行之当力。则退而行之。如着衣必煖。啖饭必饱。则实功实效。有目皆睹。人孰得以非议之哉。规矩立矣。而与巧则难。门户设矣。而能由者寡。高谈之徒及性命。讲论之不干身心。朱子当日。盖已屡形忧叹矣。然而庆元以来。至于蒙元。世犹近古。士多向里。横议不至甚炽。大义不至全乖。及夫 有明之世。尊尚表章。非不至矣。九书大全。成于馆阁。而规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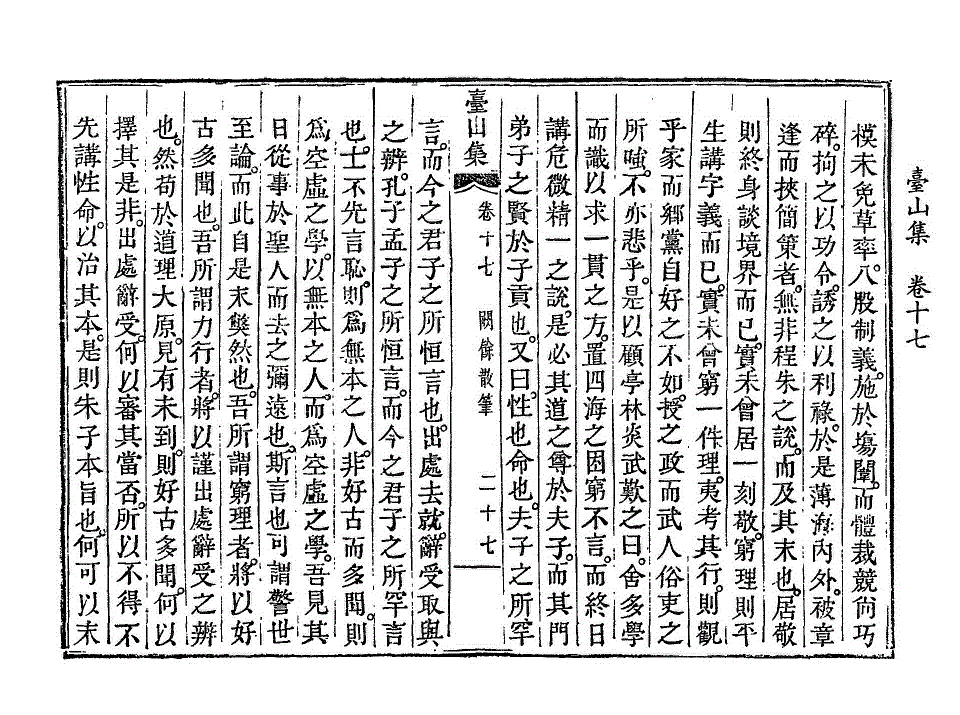 模未免草率。八股制义。施于场闱。而体裁竞尚巧碎。拘之以功令。诱之以利禄。于是薄海内外。被章逢而挟简策者。无非程朱之说。而及其末也。居敬则终身谈境界而已。实未曾居一刻敬。穷理则平生讲字义而已。实未曾穷一件理。夷考其行。则观乎家而乡党自好之不如。授之政而武人俗吏之所嗤。不亦悲乎。是以顾亭林炎武叹之曰。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尊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又曰。性也命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为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斯言也可谓警世至论。而此自是末弊然也。吾所谓穷理者。将以好古多闻也。吾所谓力行者。将以谨出处辞受之辨也。然苟于道理大原。见有未到。则好古多闻。何以择其是非。出处辞受。何以审其当否。所以不得不先讲性命。以治其本。是则朱子本旨也。何可以末
模未免草率。八股制义。施于场闱。而体裁竞尚巧碎。拘之以功令。诱之以利禄。于是薄海内外。被章逢而挟简策者。无非程朱之说。而及其末也。居敬则终身谈境界而已。实未曾居一刻敬。穷理则平生讲字义而已。实未曾穷一件理。夷考其行。则观乎家而乡党自好之不如。授之政而武人俗吏之所嗤。不亦悲乎。是以顾亭林炎武叹之曰。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尊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又曰。性也命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为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斯言也可谓警世至论。而此自是末弊然也。吾所谓穷理者。将以好古多闻也。吾所谓力行者。将以谨出处辞受之辨也。然苟于道理大原。见有未到。则好古多闻。何以择其是非。出处辞受。何以审其当否。所以不得不先讲性命。以治其本。是则朱子本旨也。何可以末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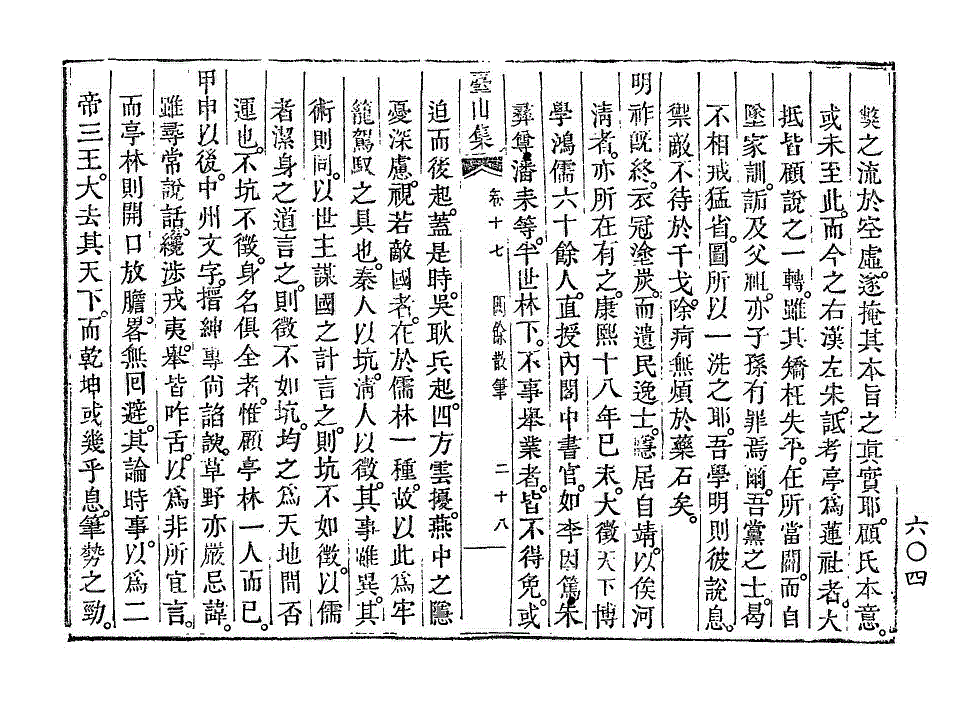 弊之流于空虚。遂掩其本旨之真实耶。顾氏本意。或未至此。而今之右汉左宋。诋考亭为莲社者。大抵皆顾说之一转。虽其矫枉失平。在所当辟。而自坠家训。诟及父祖。亦子孙有罪焉尔。吾党之士。曷不相戒猛省。图所以一洗之耶。吾学明则彼说息。御敌不待于干戈。除疴无烦于药石矣。
弊之流于空虚。遂掩其本旨之真实耶。顾氏本意。或未至此。而今之右汉左宋。诋考亭为莲社者。大抵皆顾说之一转。虽其矫枉失平。在所当辟。而自坠家训。诟及父祖。亦子孙有罪焉尔。吾党之士。曷不相戒猛省。图所以一洗之耶。吾学明则彼说息。御敌不待于干戈。除疴无烦于药石矣。明祚既终。衣冠涂炭。而遗民逸士。隐居自靖。以俟河清者。亦所在有之。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徵天下博学鸿儒六十馀人。直授内阁中书官。如李因笃,朱彝尊,潘耒等。半世林下。不事举业者。皆不得免。或迫而后起。盖是时。吴耿兵起。四方云扰。燕中之隐忧深虑。视若敌国者。在于儒林一种。故以此为牢笼驾驭之具也。秦人以坑。清人以徵。其事虽异。其术则同。以世主谋国之计言之。则坑不如徵。以儒者洁身之道言之。则徵不如坑。均之为天地间否运也。不坑不徵。身名俱全者。惟顾亭林一人而已。
甲申以后。中州文字。搢绅专尚谄谀。草野亦严忌讳。虽寻常说话。才涉戎夷。举皆咋舌。以为非所宜言。而亭林则开口放胆。略无回避。其论时事。以为二帝三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笔势之劲。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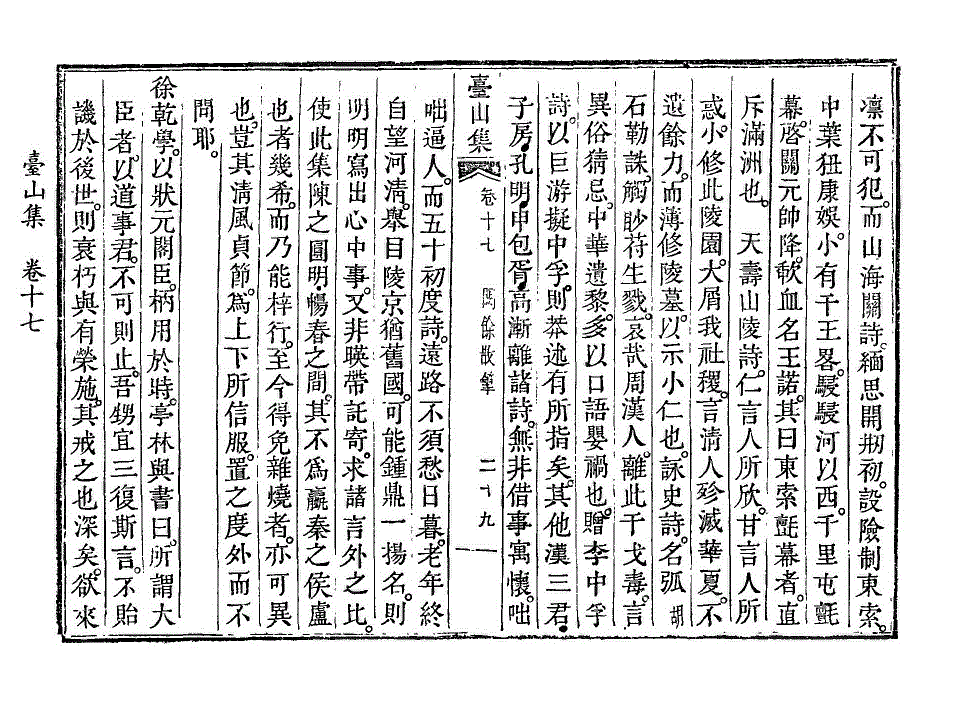 凛不可犯。而山海关诗。缅思开刱初。设险制东索。中叶狃康娱。小有干王略。骎骎河以西。千里屯毡幕。启关元帅降。歃血名王诺。其曰东索毡幕者。直斥满洲也。 天寿山陵诗。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小修此陵园。大屑我社稷。言清人殄灭华夏。不遗馀力。而薄修陵墓。以示小仁也。咏史诗。名弧(胡)石勒诛。触眇苻生戮。哀哉周汉人。离此干戈毒。言异俗猜忌。中华遗黎。多以口语婴祸也。赠李中孚诗。以巨游拟中孚。则莽述有所指矣。其他汉三君,子房,孔明,申包胥,高渐离诸诗。无非借事寓怀。咄咄逼人。而五十初度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则明明写出心中事。又非映带托寄。求诸言外之比。使此集陈之圆明,畅春之间。其不为嬴秦之侯卢也者几希。而乃能梓行。至今得免杂烧者。亦可异也。岂其清风贞节。为上下所信服。置之度外而不问耶。
凛不可犯。而山海关诗。缅思开刱初。设险制东索。中叶狃康娱。小有干王略。骎骎河以西。千里屯毡幕。启关元帅降。歃血名王诺。其曰东索毡幕者。直斥满洲也。 天寿山陵诗。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小修此陵园。大屑我社稷。言清人殄灭华夏。不遗馀力。而薄修陵墓。以示小仁也。咏史诗。名弧(胡)石勒诛。触眇苻生戮。哀哉周汉人。离此干戈毒。言异俗猜忌。中华遗黎。多以口语婴祸也。赠李中孚诗。以巨游拟中孚。则莽述有所指矣。其他汉三君,子房,孔明,申包胥,高渐离诸诗。无非借事寓怀。咄咄逼人。而五十初度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则明明写出心中事。又非映带托寄。求诸言外之比。使此集陈之圆明,畅春之间。其不为嬴秦之侯卢也者几希。而乃能梓行。至今得免杂烧者。亦可异也。岂其清风贞节。为上下所信服。置之度外而不问耶。徐乾学。以状元阁臣。柄用于时。亭林与书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其戒之也深矣。欲来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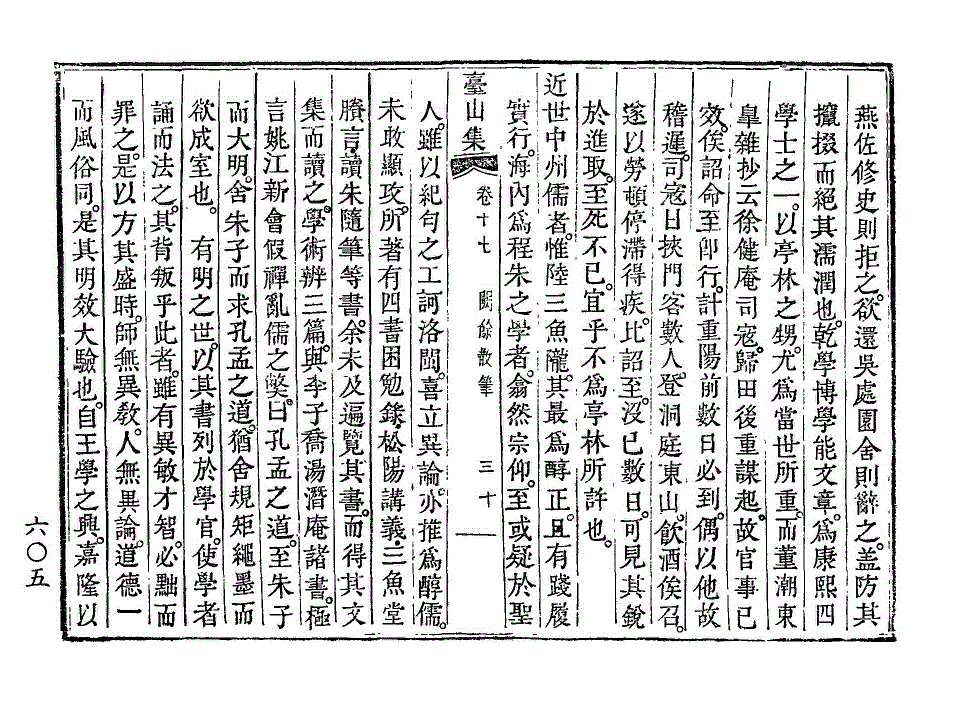 燕佐修史则拒之。欲还吴处园舍则辞之。盖防其撺掇而绝其濡润也。乾学博学能文章。为康熙四学士之一。以亭林之甥。尤为当世所重。而董潮东皋杂抄云徐健庵司寇。归田后重谋起。故官事已效。俟诏命至即行。计重阳前数日必到。偶以他故稽迟。司寇日挟门客数人。登洞庭东山。饮酒俟召。遂以劳顿停滞得疾。比诏至。没已数日。可见其锐于进取。至死不已。宜乎不为亭林所许也。
燕佐修史则拒之。欲还吴处园舍则辞之。盖防其撺掇而绝其濡润也。乾学博学能文章。为康熙四学士之一。以亭林之甥。尤为当世所重。而董潮东皋杂抄云徐健庵司寇。归田后重谋起。故官事已效。俟诏命至即行。计重阳前数日必到。偶以他故稽迟。司寇日挟门客数人。登洞庭东山。饮酒俟召。遂以劳顿停滞得疾。比诏至。没已数日。可见其锐于进取。至死不已。宜乎不为亭林所许也。近世中州儒者。惟陆三鱼陇其。最为醇正。且有践履实行。海内为程朱之学者。翕然宗仰。至或疑于圣人。虽以纪匀之工诃洛闽。喜立异论。亦推为醇儒。未敢显攻。所著有四书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剩言,读朱随笔等书。余未及遍览其书。而得其文集而读之。学术辨三篇。与李子乔汤潜庵诸书。极言姚江新会假禅乱儒之弊。曰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舍朱子而求孔孟之道。犹舍规矩绳墨而欲成室也。 有明之世。以其书列于学官。使学者诵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虽有异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是以方其盛时。师无异教。人无异论。道德一而风俗同。是其明效大验也。自王学之兴。嘉隆以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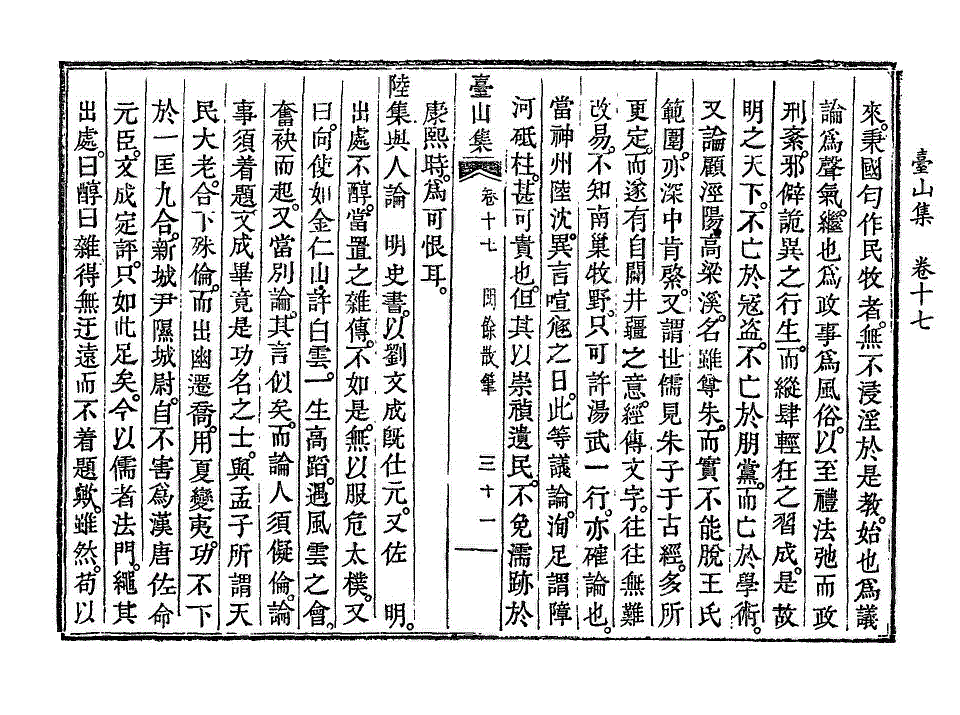 来。秉国匀作民牧者。无不浸淫于是教。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为政事为风俗。以至礼法弛而政刑紊。邪僻诡异之行生。而纵肆轻狂之习成。是故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又论顾泾阳,高梁溪。名虽尊朱。而实不能脱王氏范围。亦深中肯綮。又谓世儒见朱子于古经。多所更定。而遂有自辟井疆之意。经传文字。往往无难改易。不知南巢牧野。只可许汤武一行。亦确论也。当神州陆沈。异言喧䝇之日。此等议论。洵足谓障河砥柱。甚可贵也。但其以崇祯遗民。不免濡迹于康熙时。为可恨耳。
来。秉国匀作民牧者。无不浸淫于是教。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为政事为风俗。以至礼法弛而政刑紊。邪僻诡异之行生。而纵肆轻狂之习成。是故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又论顾泾阳,高梁溪。名虽尊朱。而实不能脱王氏范围。亦深中肯綮。又谓世儒见朱子于古经。多所更定。而遂有自辟井疆之意。经传文字。往往无难改易。不知南巢牧野。只可许汤武一行。亦确论也。当神州陆沈。异言喧䝇之日。此等议论。洵足谓障河砥柱。甚可贵也。但其以崇祯遗民。不免濡迹于康熙时。为可恨耳。陆集与人论 明史书。以刘文成既仕元。又佐 明。出处不醇。当置之杂传。不如是。无以服危太朴。又曰。向使如金仁山,许白云。一生高蹈。遇风云之会。奋袂而起。又当别论。其言似矣。而论人须儗伦。论事须着题文成毕竟是功名之士。与孟子所谓天民大老。合下殊伦。而出幽迁乔。用夏变夷。功不下于一匡九合。新城尹隰城尉。自不害为汉唐佐命元臣。文成定评。只如此足矣。今以儒者法门。绳其出处。曰醇曰杂得无迂远而不着题欤。虽然。苟以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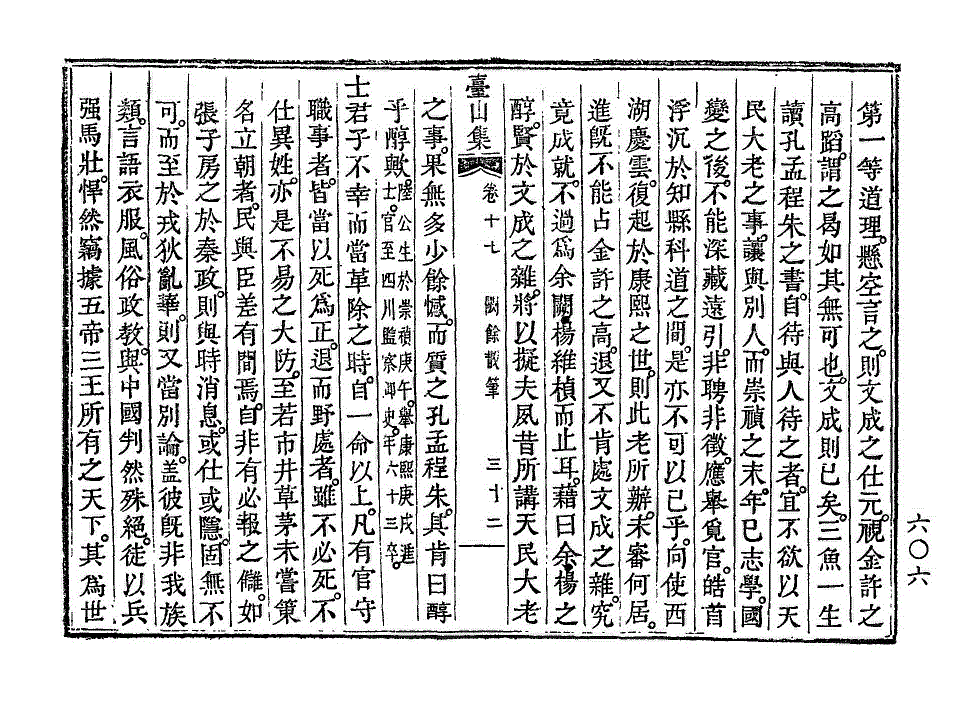 第一等道理。悬空言之。则文成之仕元。视金许之高蹈。谓之曷如其无可也。文成则已矣。三鱼一生读孔孟程朱之书。自待与人待之者。宜不欲以天民大老之事。让与别人。而崇祯之末。年已志学。国变之后。不能深藏远引。非聘非徵。应举觅官。皓首浮沉于知县科道之间。是亦不可以已乎。向使西湖庆云。复起于康熙之世。则此老所办。未审何居。进既不能占金许之高。退又不肯处文成之杂。究竟成就。不过为余阙,杨维桢而止耳。藉曰余,杨之醇。贤于文成之杂。将以拟夫夙昔所讲天民大老之事。果无多少馀憾。而质之孔孟程朱。其肯曰醇乎醇欤。(陆公生于崇祯庚午。举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年六十三卒。)
第一等道理。悬空言之。则文成之仕元。视金许之高蹈。谓之曷如其无可也。文成则已矣。三鱼一生读孔孟程朱之书。自待与人待之者。宜不欲以天民大老之事。让与别人。而崇祯之末。年已志学。国变之后。不能深藏远引。非聘非徵。应举觅官。皓首浮沉于知县科道之间。是亦不可以已乎。向使西湖庆云。复起于康熙之世。则此老所办。未审何居。进既不能占金许之高。退又不肯处文成之杂。究竟成就。不过为余阙,杨维桢而止耳。藉曰余,杨之醇。贤于文成之杂。将以拟夫夙昔所讲天民大老之事。果无多少馀憾。而质之孔孟程朱。其肯曰醇乎醇欤。(陆公生于崇祯庚午。举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年六十三卒。)士君子不幸而当革除之时。自一命以上。凡有官守职事者。皆当以死为正。退而野处者。虽不必死。不仕异姓。亦是不易之大防。至若韨井草茅未尝策名立朝者。民与臣差有间焉。自非有必报之雠。如张子房之于秦政。则与时消息。或仕或隐。固无不可。而至于戎狄乱华。则又当别论。盖彼既非我族类。言语衣服。风俗政教。与中国判然殊绝。徒以兵强马壮。悍然窃据五帝三王所有之天下。其为世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7H 页
 变。果何如也。六朝五季。皆以篡夺得国。岂曰正矣。而废兴代谢。俱不出先王声教之内。则方之于彼。犹为常理顺境耳。不幸之极。遇此时节。则君子之洁身制行。视寻常革除。当加严一等。苟其生长闻见。仅能及于中华义主之世者。皆当没齿自靖。矢心罔仆。不得以民臣之说曲辨而强别之也。常调杂流。一切以功名利禄为事者。固难以斯义律之也。名为儒者。忽此而不之省。则大节差矣。仁义礼乐。都归空言。孝弟忠信。皆属细行。吾何以观之哉。被发左衽。何妨于为圣为贤。而吾夫子恐恐然有微管之叹何也。春秋之义。责贤者备。贤如稼书。不得不责之备也。
变。果何如也。六朝五季。皆以篡夺得国。岂曰正矣。而废兴代谢。俱不出先王声教之内。则方之于彼。犹为常理顺境耳。不幸之极。遇此时节。则君子之洁身制行。视寻常革除。当加严一等。苟其生长闻见。仅能及于中华义主之世者。皆当没齿自靖。矢心罔仆。不得以民臣之说曲辨而强别之也。常调杂流。一切以功名利禄为事者。固难以斯义律之也。名为儒者。忽此而不之省。则大节差矣。仁义礼乐。都归空言。孝弟忠信。皆属细行。吾何以观之哉。被发左衽。何妨于为圣为贤。而吾夫子恐恐然有微管之叹何也。春秋之义。责贤者备。贤如稼书。不得不责之备也。顾亭林日知录曰。五经无真字。见于老庄之书。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书真秦之声也。韩信传。即为真王耳。窦融上光武书。岂可背真旧之主。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间。学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会试论语题。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庄子大宗师篇云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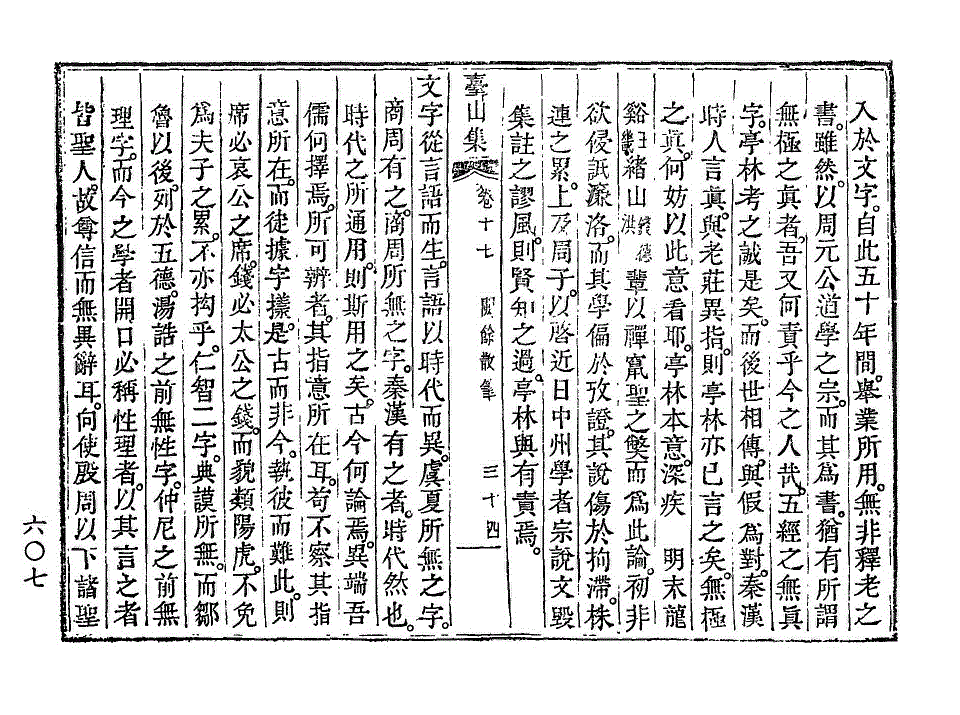 入于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五经之无真字。亭林考之诚是矣。而后世相传。与假为对。秦汉时人言真。与老庄异指。则亭林亦已言之矣。无极之真。何妨以此意看耶。亭林本意。深疾 明末龙溪(王畿),绪山(钱德洪)辈以禅窜圣之弊而为此论。初非欲侵诋濂洛。而其学偏于考證。其说伤于拘滞。株连之累。上及周子。以启近日中州学者宗说文毁集注之谬风。则贤知之过。亭林与有责焉。
入于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五经之无真字。亭林考之诚是矣。而后世相传。与假为对。秦汉时人言真。与老庄异指。则亭林亦已言之矣。无极之真。何妨以此意看耶。亭林本意。深疾 明末龙溪(王畿),绪山(钱德洪)辈以禅窜圣之弊而为此论。初非欲侵诋濂洛。而其学偏于考證。其说伤于拘滞。株连之累。上及周子。以启近日中州学者宗说文毁集注之谬风。则贤知之过。亭林与有责焉。文字从言语而生。言语以时代而异。虞夏所无之字。商周有之。商周所无之字。秦汉有之者。时代然也。时代之所通用。则斯用之矣。古今何论焉。异端吾儒何择焉。所可辨者。其指意所在耳。苟不察其指意所在。而徒据字㨾。是古而非今。执彼而难此。则席必哀公之席。钱必太公之钱。而貌类阳虎。不免为夫子之累。不亦拘乎。仁智二字。典谟所无。而邹鲁以后。列于五德。汤诰之前无性字。仲尼之前无理字。而今之学者开口必称性理者。以其言之者皆圣人。故尊信而无异辞耳。向使殷周以下诸圣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8H 页
 人。不甚尊信。而有一考證者出于其间。颛颛然执古今以为与夺。则仁智性理等字之无于典谟。其为可议。何异于真字之无于五经耶。或曰。亭林之恶真字。以其始见于老庄之书。吾儒不当袭用也。今子以经文圣训之古无今有者。引而相难。何其言之疏而辨之强耶。曰吾将毕其说。夫所谓异端之书。吾儒不当袭用者。字㨾云乎。指意云乎。如曰字㨾云乎。则不惟见于彼书者。吾不当袭用。虽见于吾书者。一经彼用。皆当讳而避之耶。道德二字。老氏建为宗旨。而赞尧授禹。其文则同。易言寂。孟子言觉。曰寂曰觉。皆禅书中语也。子将何以处之。如曰吾之所谓寂觉。与彼之所谓寂觉。字同而指不同也云尔。则吾亦曰周子之真。与老庄之真。字同而指不同也。觉者佛之翻义也。孟子言之。则不疑其涉禅。真者实之代训也。周子言之。则疑其袭庄。岂亦以时世之远近而上下其手耶。
人。不甚尊信。而有一考證者出于其间。颛颛然执古今以为与夺。则仁智性理等字之无于典谟。其为可议。何异于真字之无于五经耶。或曰。亭林之恶真字。以其始见于老庄之书。吾儒不当袭用也。今子以经文圣训之古无今有者。引而相难。何其言之疏而辨之强耶。曰吾将毕其说。夫所谓异端之书。吾儒不当袭用者。字㨾云乎。指意云乎。如曰字㨾云乎。则不惟见于彼书者。吾不当袭用。虽见于吾书者。一经彼用。皆当讳而避之耶。道德二字。老氏建为宗旨。而赞尧授禹。其文则同。易言寂。孟子言觉。曰寂曰觉。皆禅书中语也。子将何以处之。如曰吾之所谓寂觉。与彼之所谓寂觉。字同而指不同也云尔。则吾亦曰周子之真。与老庄之真。字同而指不同也。觉者佛之翻义也。孟子言之。则不疑其涉禅。真者实之代训也。周子言之。则疑其袭庄。岂亦以时世之远近而上下其手耶。亭林虽力斥真字之不经。而自家亦不免承用。日知录卷之十九云世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有知言者出。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
台山集卷十七 第 6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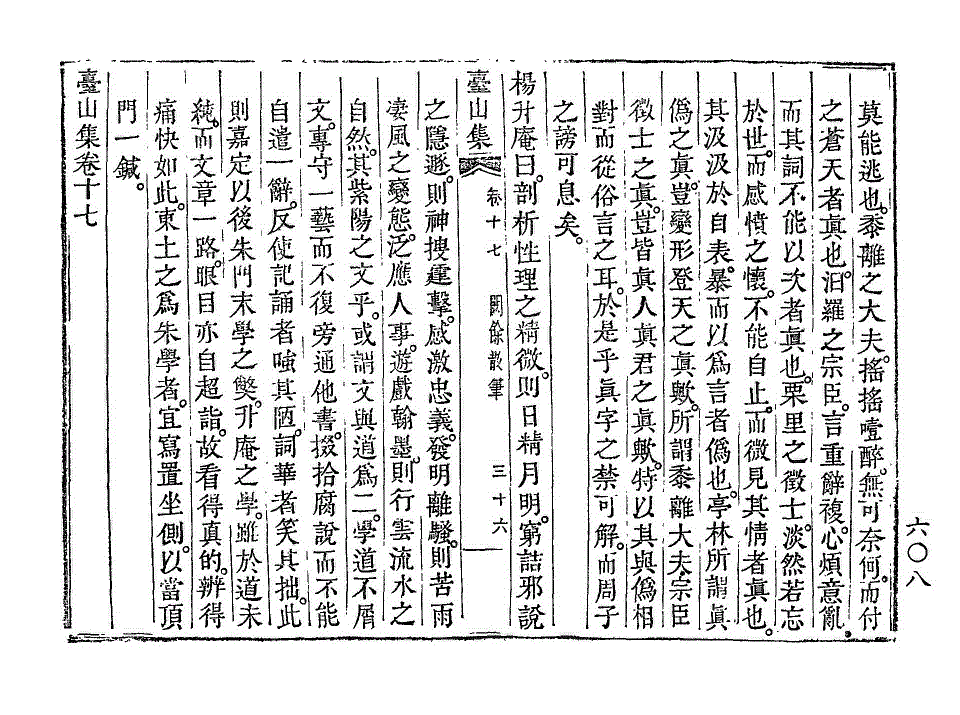 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摇摇噎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重辞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以为言者伪也。亭林所谓真伪之真。岂变形登天之真欤。所谓黍离大夫,宗臣徵士之真。岂皆真人真君之真欤。特以其与伪相对而从俗言之耳。于是乎真字之禁可解。而周子之谤可息矣。
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摇摇噎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重辞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以为言者伪也。亭林所谓真伪之真。岂变形登天之真欤。所谓黍离大夫,宗臣徵士之真。岂皆真人真君之真欤。特以其与伪相对而从俗言之耳。于是乎真字之禁可解。而周子之谤可息矣。杨升庵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感激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其紫阳之文乎。或谓文与道为二。学道不屑文。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使记诵者嗤其陋。词华者笑其拙。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升庵之学。虽于道未纯。而文章一路。眼目亦自超诣。故看得真的。辨得痛快如此。东土之为朱学者。宜写置坐侧。以当顶门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