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x 页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丰山 洪奭周成伯 著)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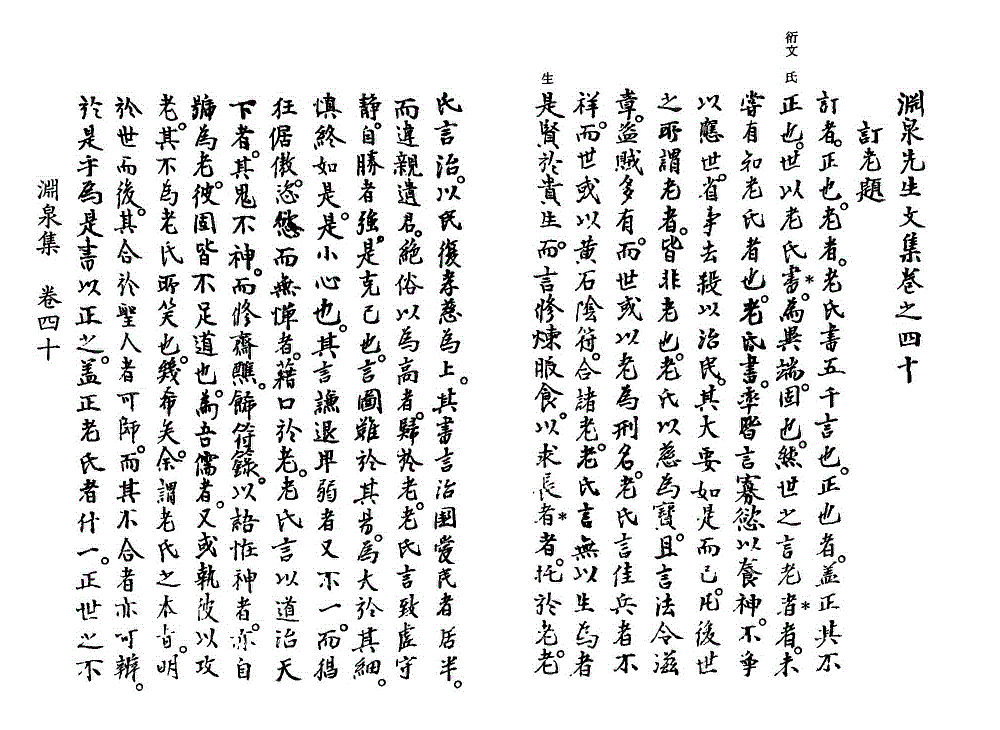 订老题
订老题订者。正也。老者。老氏书五千言也。正也者。盖正其不正也。世以老氏。为异端。固也。然世之言老氏者。未尝有知老氏者也。老氏书。率皆言寡欲以养神。不争以应世。省事去杀以治民。其大要如是而已。凡后世之所谓老者。皆非老也。老氏以慈为宝。且言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而世或以老为刑名。老氏言佳兵者不祥。而世或以黄石阴符。合诸老。老氏言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而言修炼服食。以求长生者。托于老。老氏言治。以民复孝慈为上。其书言治国爱民者居半。而违亲遗君。绝俗以为高者。归于老。老氏言致虚守静。自胜者强。是克己也。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慎终如是。是小心也。其言谦退卑弱者又不一。而猖狂倨傲。恣欲而无惮者。藉口于老。老氏言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而修斋醮。饰符箓。以语怪神者。亦自号为老。彼固皆不足道也。为吾儒者。又或执彼以攻老。其不为老氏所笑也。几希矣。余谓老氏之本旨。明于世而后。其合于圣人者可师。而其不合者亦可辨。于是乎为是书以正之。盖正老氏者什一。正世之不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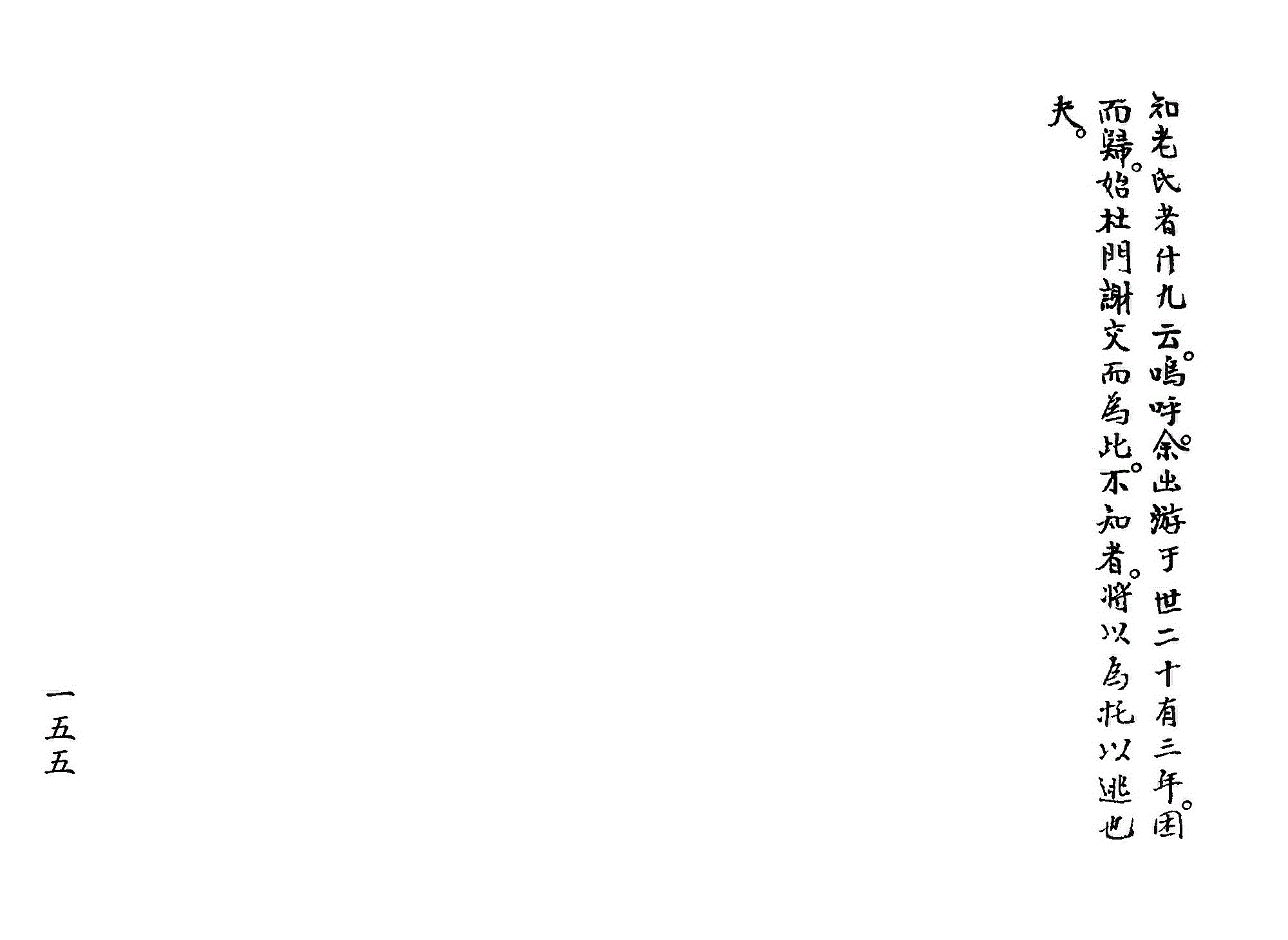 知老氏者什九云。呜呼。余出游于世二十有三年。困而归。始杜门谢交而为此。不知者。将以为托以逃也夫。
知老氏者什九云。呜呼。余出游于世二十有三年。困而归。始杜门谢交而为此。不知者。将以为托以逃也夫。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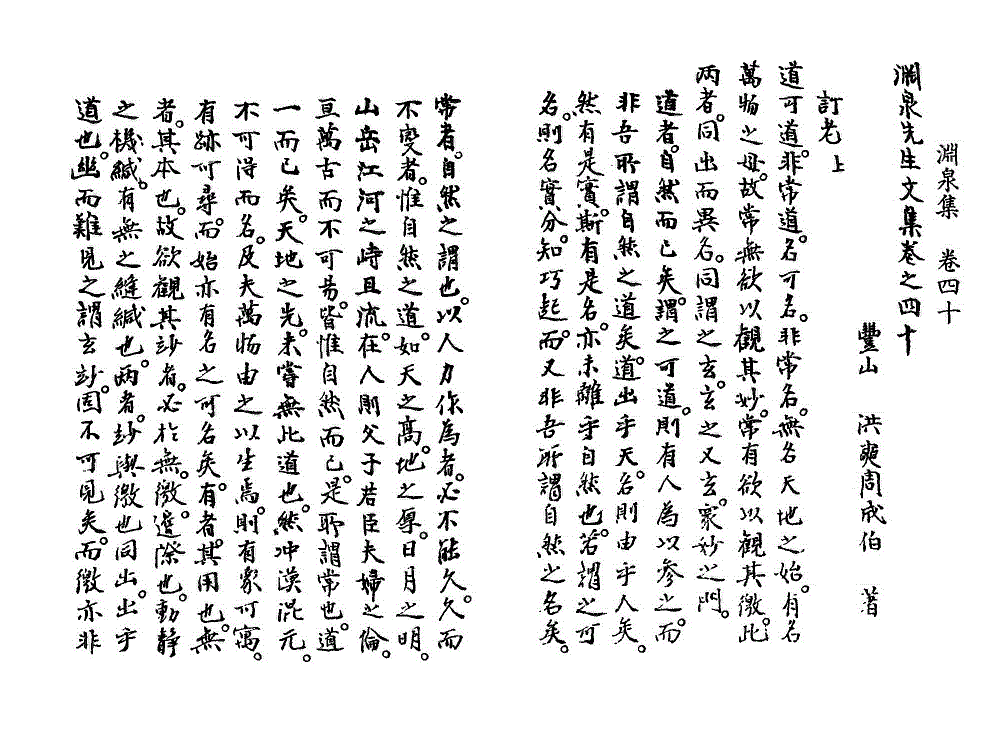 订老[上]
订老[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者。自然而已矣。谓之可道。则有人为以参之。而非吾所谓自然之道矣。道出乎天。名则由乎人矣。然有是实。斯有是名。亦未离乎自然也。若谓之可名。则名实分。知巧起。而又非吾所谓自然之名矣。常者。自然之谓也。以人力作为者。必不能久。久而不变者。惟自然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山岳江河之峙且流。在人则父子君臣夫妇之伦。亘万古而不可易。皆惟自然而已。是所谓常也。道一而已矣。天地之先。未尝无此道也。然冲漠混元。不可得而名。及夫万物由之以生焉。则有象可寓。有迹可寻。而始亦有名之可名矣。有者。其用也。无者。其本也。故欲观其妙者。必于无。徼。边际也。动静之机缄。有无之缝缄也。两者。妙与徼也同出。出乎道也。幽而难见之谓玄妙。固不可见矣。而徼亦非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6L 页
 有声臭色象之著。故同谓之玄也。玄之又玄。重言以赞叹之也。道之妙。亦一而已。然散在万物。而万物皆有是道。此所谓众妙也。门所由出也。万物固莫不由是道。然其所由出则一而已。而所谓一者。不可见。此易所谓太极。子思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周子所谓无极之真。程子所谓冲漠无眹也。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夫自然之谓道。当行之亦谓道。是二者。未始有异道也。故老子之所谓道。与孔子子思之所谓道。亦未始异也。然孔子子思之语道也。显而示之以当行之则。其行之也。又恒不越乎人伦日用之近且切也。故其为教百世而无弊。老子之语道也。推而极之于自然之妙。其为说。又恒若恍惚而不可测。此所以一再转而为谲诡荒唐者所假托也。孔子子思。亦何尝不语自然哉。其言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无思也。无为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夫如是而已。老子之书。一则曰无。二则曰玄。夫以形言则自无而有。固也。不知其理之未尝一日无也。言乎其微而不可见者。则谓之玄。亦固也。不知其坦然而可行者。未始不昭昭
有声臭色象之著。故同谓之玄也。玄之又玄。重言以赞叹之也。道之妙。亦一而已。然散在万物。而万物皆有是道。此所谓众妙也。门所由出也。万物固莫不由是道。然其所由出则一而已。而所谓一者。不可见。此易所谓太极。子思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周子所谓无极之真。程子所谓冲漠无眹也。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夫自然之谓道。当行之亦谓道。是二者。未始有异道也。故老子之所谓道。与孔子子思之所谓道。亦未始异也。然孔子子思之语道也。显而示之以当行之则。其行之也。又恒不越乎人伦日用之近且切也。故其为教百世而无弊。老子之语道也。推而极之于自然之妙。其为说。又恒若恍惚而不可测。此所以一再转而为谲诡荒唐者所假托也。孔子子思。亦何尝不语自然哉。其言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无思也。无为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夫如是而已。老子之书。一则曰无。二则曰玄。夫以形言则自无而有。固也。不知其理之未尝一日无也。言乎其微而不可见者。则谓之玄。亦固也。不知其坦然而可行者。未始不昭昭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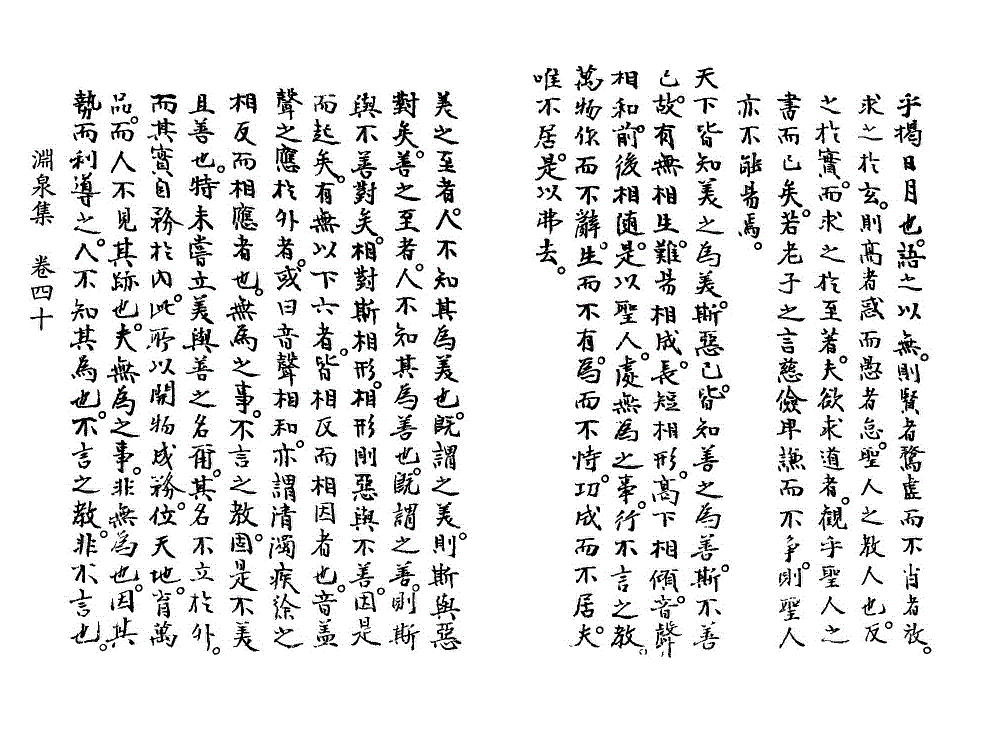 乎揭日月也。语之以无。则贤者骛虚而不肖者放。求之于玄。则高者惑而愚者怠。圣人之教人也。反之于实。而求之于至著。夫欲求道者。观乎圣人之书而已矣。若老子之言慈俭卑谦而不争。则圣人亦不能易焉。
乎揭日月也。语之以无。则贤者骛虚而不肖者放。求之于玄。则高者惑而愚者怠。圣人之教人也。反之于实。而求之于至著。夫欲求道者。观乎圣人之书而已矣。若老子之言慈俭卑谦而不争。则圣人亦不能易焉。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弗去。
美之至者。人不知其为美也。既谓之美。则斯与恶对矣。善之至者。人不知其为善也。既谓之善。则斯与不善对矣。相对斯相形。相形则恶与不善。因是而起矣。有无以下六者。皆相反而相因者也。音盖声之应于外者。或曰音声相和。亦谓清浊疾徐之相反而相应者也。无为之事。不言之教。固是不美且善也。特未尝立美与善之名尔。其名不立于外。而其实自务于内。此所以开物成务。位天地。育万品。而人不见其迹也。夫无为之事。非无为也。因其势而利导之。人不知其为也。不言之教。非不言也。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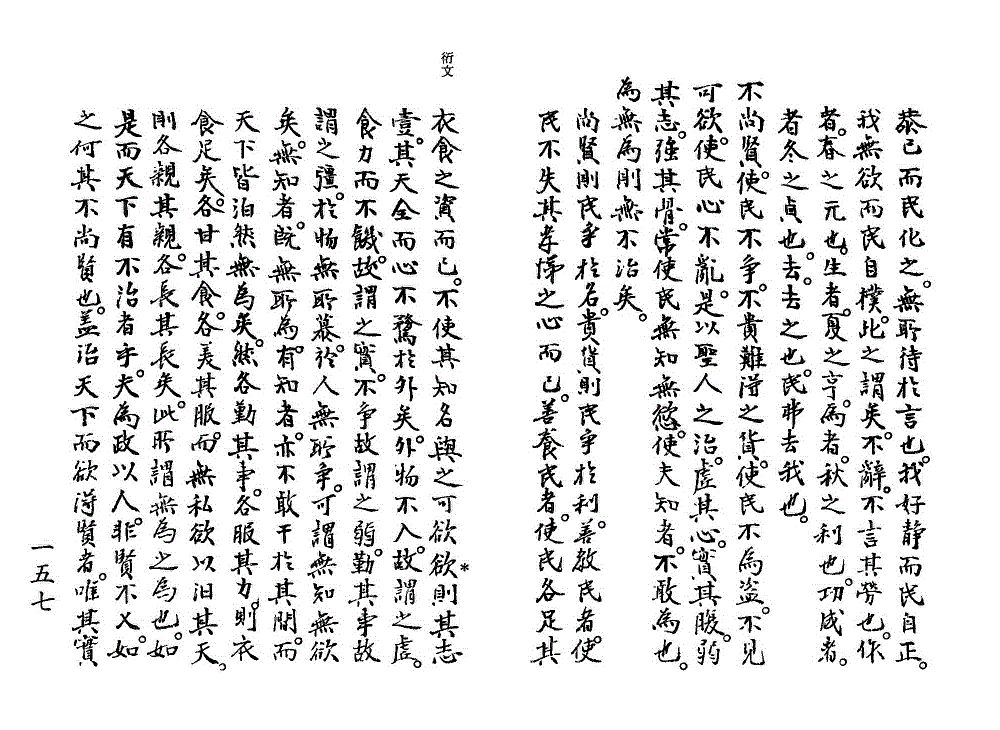 恭己而民化之。无所待于言也。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此之谓矣。不辞。不言其劳也。作者。春之元也。生者。夏之亨。为者。秋之利也。功成者。者(者衍字)冬之贞也。去。去之也。民弗去我也。
恭己而民化之。无所待于言也。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此之谓矣。不辞。不言其劳也。作者。春之元也。生者。夏之亨。为者。秋之利也。功成者。者(者衍字)冬之贞也。去。去之也。民弗去我也。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尚贤则民争于名。贵货则民争于利。善教民者。使民不失其孝悌之心而已。善养民者。使民各足其衣食之资而已。不使其知名与之可欲则其志壹。其天全而心不骛于外矣。外物不入。故谓之虚。食力而不饥。故谓之实。不争故谓之弱。勒其事故谓之彊。于物无所慕。于人无所争。可谓无知无欲矣。无知者。既无所为。有知者。亦不敢干于其间。而天下皆泊然无为矣。然各勤其事。各服其力。则衣食足矣。各甘其食。各美其服。而无私欲以汩其天。则各亲其亲。各长其长矣。此所谓无为之为也。如是而天下有不治者乎。夫为政以人。非贤不乂。如之何其不尚贤也。盖治天下而欲得贤者。唯其实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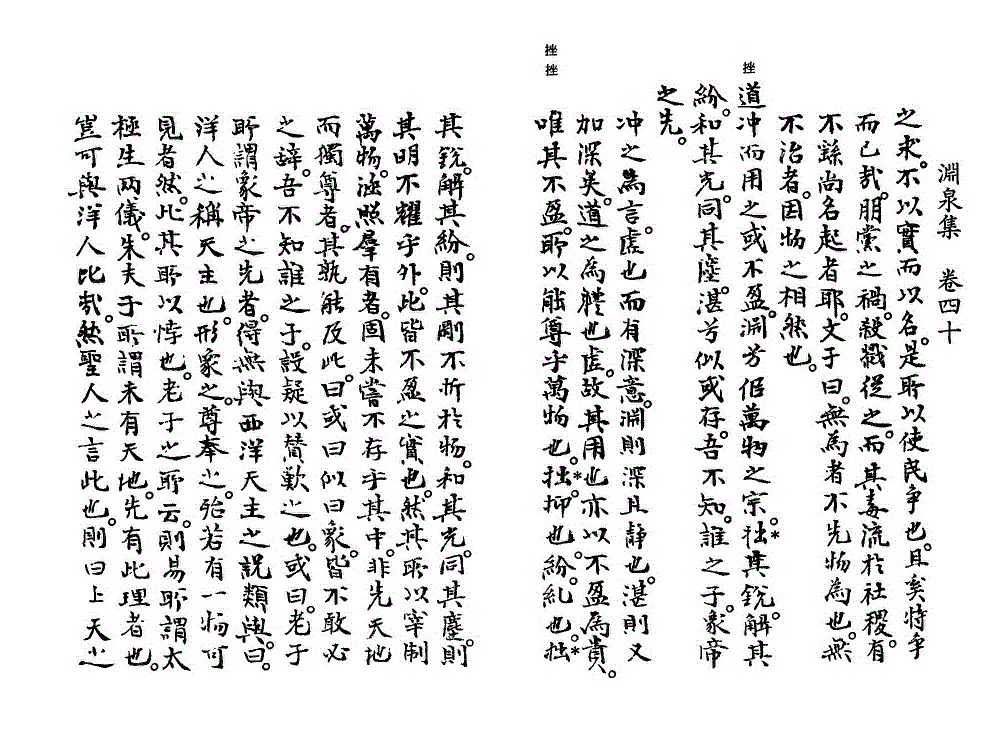 之求。不以实而以名。是所以使民争也。且奚特争而已哉。朋党之祸。杀戮从之。而其毒流于社稷。有不繇尚名起者耶。文子曰。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之求。不以实而以名。是所以使民争也。且奚特争而已哉。朋党之祸。杀戮从之。而其毒流于社稷。有不繇尚名起者耶。文子曰。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冲之为言。虚也而有深意。渊则深且静也。湛则又加深矣。道之为体也虚。故其用也亦以不盈为贵。唯其不盈。所以能尊乎万物也。挫。抑也。纷。糺也。挫其锐。解其纷。则其刚不折于物。和其光。同其尘。则其明不耀乎外。此皆不盈之实也。然其所以宰制万物。涵照群有者。固未尝不存乎其中。非先天地而独尊者。其孰能及此。曰或曰似曰象。皆不敢必之辞。吾不知谁之子。设疑以赞叹之也。或曰。老子所谓象帝之先者。得无与西洋天主之说类与。曰。洋人之称天主也。形象之。尊奉之。殆若有一物可见者然。此其所以悖也。老子之所云。则易所谓太极生两仪。朱夫子所谓未有天地。先有此理者也。岂可与洋人比哉。然圣人之言此也。则曰上天之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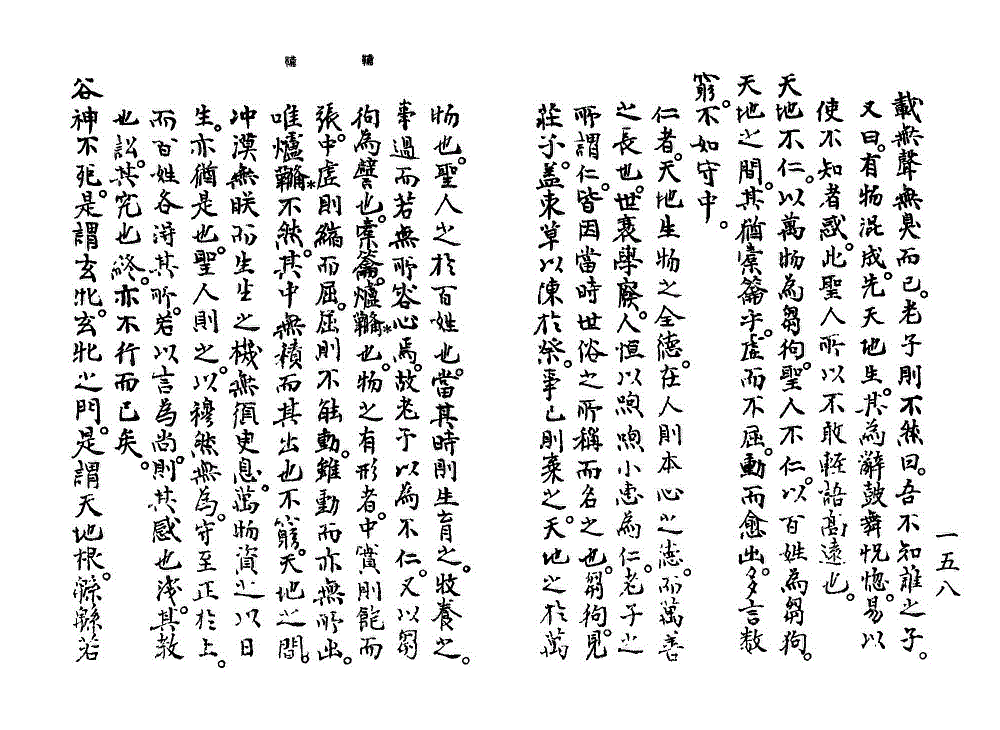 载无声无臭而已。老子则不然曰。吾不知谁之子。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为辞鼓舞恍惚。易以使不知者惑。此圣人所以不敢轻语高远也。
载无声无臭而已。老子则不然曰。吾不知谁之子。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为辞鼓舞恍惚。易以使不知者惑。此圣人所以不敢轻语高远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仁者。天地生物之全德。在人则本心之德。而万善之长也。世衰学废。人恒以喣喣小惠为仁。老子之所谓仁。皆因当时世俗之所称而名之也。刍狗。见庄子。盖束草以陈于祭。事已则弃之。天地之于万物也。圣人之于百姓也。当其时则生育之。牧养之。事过而若无所容心焉。故老子以为不仁。又以刍狗为譬也。橐籥。炉鞴也。物之有形者。中实则饱而张。中虚则缩而屈。屈则不能动。虽动而亦无所出。唯炉鞴不然。其中无积而其出也不穷。天地之间。冲漠无眹而生生之机无须臾息。万物资之以日生。亦犹是也。圣人则之。以穆然无为。守至正于上。而百姓各得其所。若以言为尚。则其感也浅。其教也讼。其究也终。亦不行而已矣。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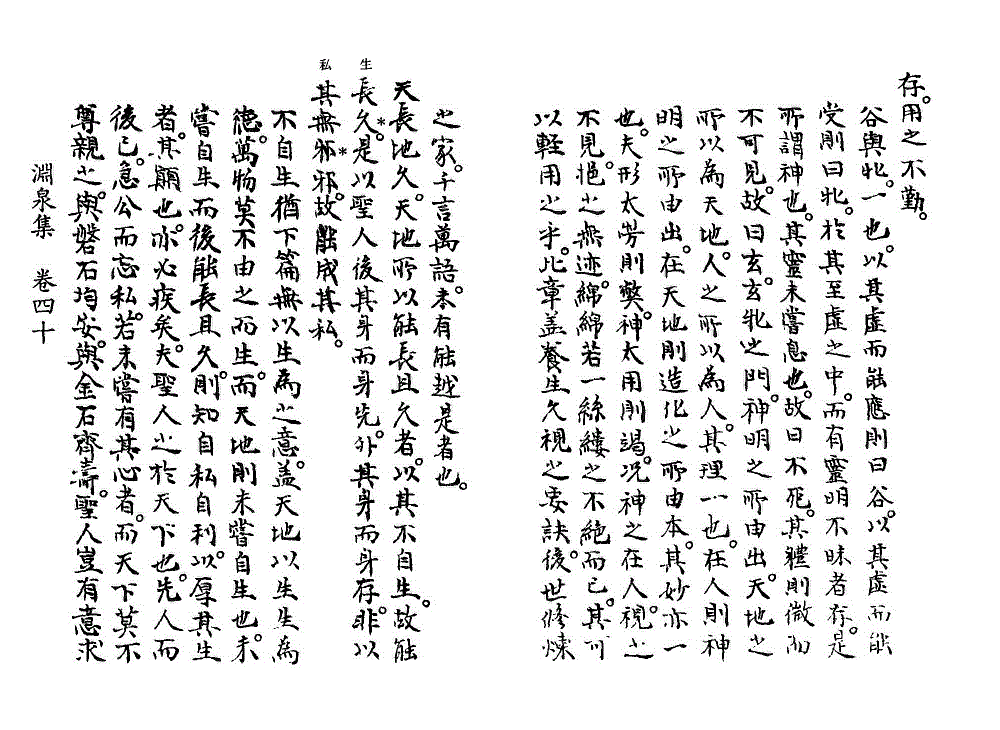 存。用之不勤。
存。用之不勤。谷与牝。一也。以其虚而能应则曰谷。以其虚而能受则曰牝。于其至虚之中。而有灵明不昧者存。是所谓神也。其灵未尝息也。故曰不死。其体则微而不可见。故曰玄。玄牝之门。神明之所由出。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人之所以为人。其理一也。在人则神明之所由出。在天地则造化之所由本。其妙亦一也。夫形太劳则弊。神太用则竭。况神之在人。视之不见。挹之无迹。绵绵若一丝缕之不绝而已。其可以轻用之乎。此章盖养生久视之要诀。后世修炼之家。千言万语。未有能越是者也。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不自生犹下篇无以生为之意。盖天地以生生为德。万物莫不由之而生。而天地则未尝自生也。未尝自生而后能长且久。则知自私自利。以厚其生者。其颠也。亦必疾矣。夫圣人之于天下也。先人而后己。急公而忘私。若未尝有其心者。而天下莫不尊亲之。与磐石均安。与金石齐寿。圣人岂有意求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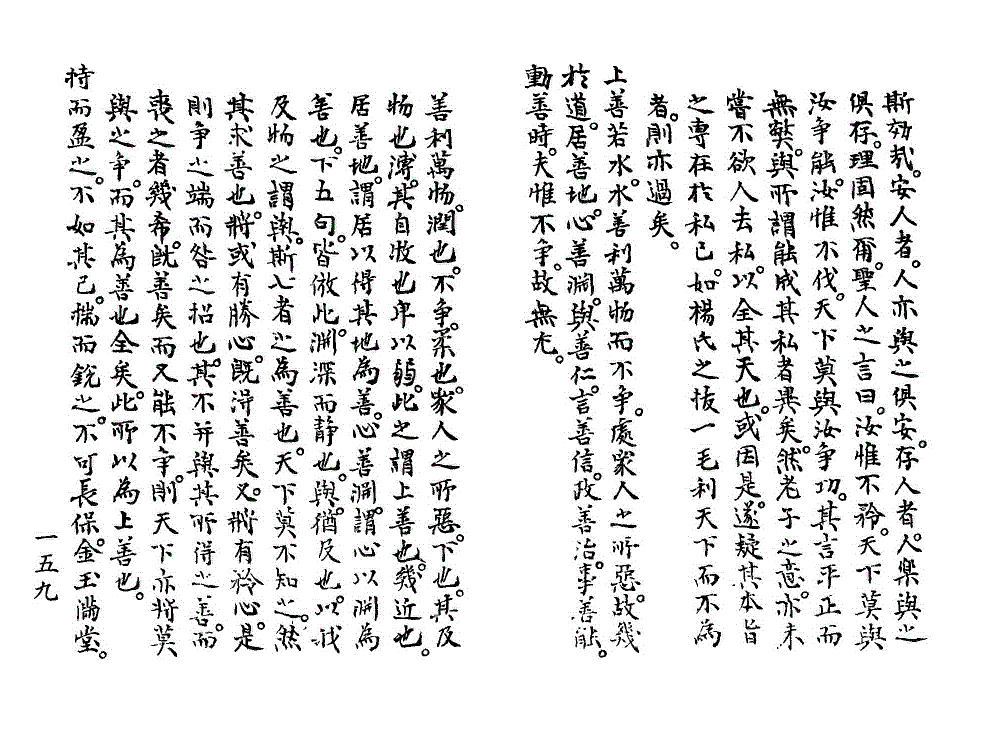 斯效哉。安人者。人亦与之俱安。存人者。人乐与之俱存。理固然尔。圣人之言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其言平正而无弊。与所谓能成其私者异矣。然老子之意。亦未尝不欲人去私。以全其天也。或因是。遂疑其本旨之专在于私己。如杨氏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则亦过矣。
斯效哉。安人者。人亦与之俱安。存人者。人乐与之俱存。理固然尔。圣人之言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其言平正而无弊。与所谓能成其私者异矣。然老子之意。亦未尝不欲人去私。以全其天也。或因是。遂疑其本旨之专在于私己。如杨氏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则亦过矣。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善利万物。润也。不争。柔也。众人之所恶。下也。其及物也溥。其自牧也卑以弱。此之谓上善也。几近也。居善地。谓居以得其地为善。心善渊。谓心以渊为善也。下五句。皆仿此。渊深而静也。与。犹及也。以我及物之谓与。斯七者之为善也。天下莫不知之。然其求善也。将或有胜心。既得善矣。又将有矜心。是则争之端而咎之招也。其不并与其所得之善。而丧之者几希。既善矣而又能不争。则天下亦将莫与之争。而其为善也全矣。此所以为上善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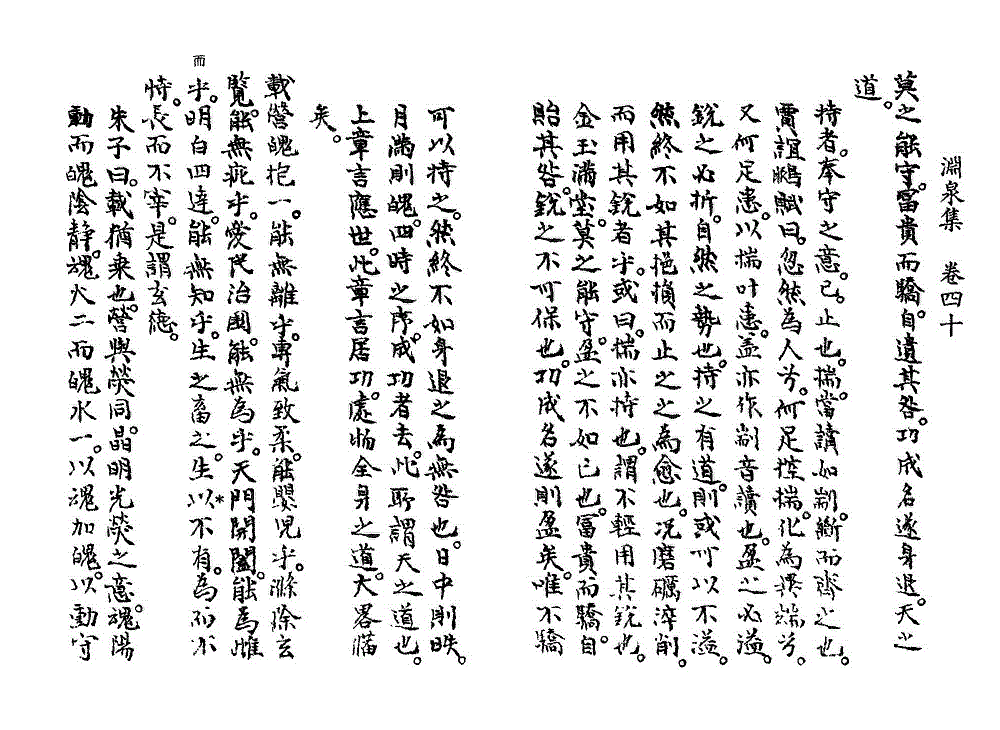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持者。奉守之意。已。止也。揣。当读如剬。断而齐之也。贾谊鵩赋曰。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揣。化为异端兮。又何足患。以揣叶患。盖亦作剬音读也。盈之必溢。锐之必折。自然之势也。持之有道。则或可以不溢。然终不如其挹损而止之之为愈也。况磨砺淬削。而用其锐者乎。或曰。揣亦持也。谓不轻用其锐也。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盈之不如已也。富贵而骄。自贻其咎。锐之不可保也。功成名遂则盈矣。唯不骄可以持之。然终不如身退之为无咎也。日中则昳。月满则魄。四时之序。成功者去。此所谓天之道也。上章言应世。此章言居功。处物全身之道。大略备矣。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朱子曰。载犹乘也。营与荧同。晶明光荧之意。魂阳动而魄阴静。魂火二而魄水一。以魂加魄。以动守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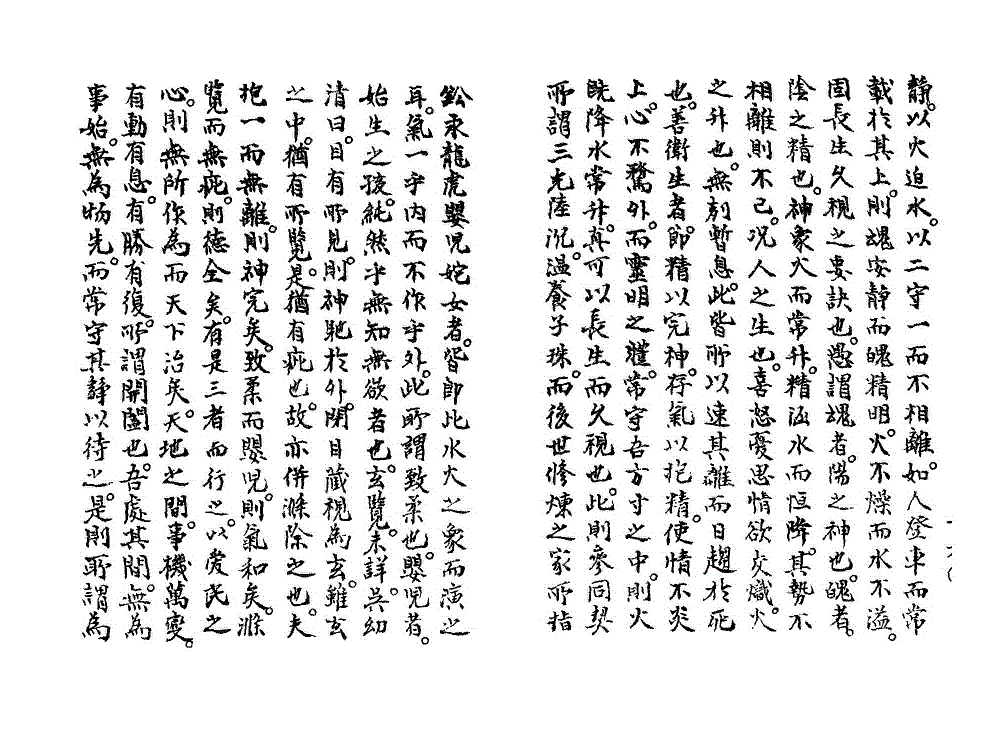 静。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离。如人登车而常载于其上。则魂安静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长生久视之要诀也。愚谓魂者。阳之神也。魄者。阴之精也。神象火而常升。精涵水而恒降。其势不相离则不已。况人之生也。喜怒忧思情欲交炽。火之升也。无刻暂息。此皆所以速其离而日趋于死也。善卫生者。节精以完神。存气以抱精。使情不炎上。心不骛外。而灵明之体。常守吾方寸之中。则火既降水常升。真可以长生而久视也。此则参同契所谓三光陆沉。温养子珠。而后世修炼之家所指铅汞龙虎婴儿姹女者。皆即此水火之象而演之耳。气一乎内而不作乎外。此所谓致柔也。婴儿者。始生之孩。纯然乎无知无欲者也。玄览。未详。吴幼清曰。目有所见。则神驰于外。闭目藏视为玄。虽玄之中。犹有所览。是犹有疵也。故亦并涤除之也。夫抱一而无离。则神完矣。致柔而婴儿。则气和矣。涤览而无疵。则德全矣。有是三者而行之。以爱民之心。则无所作为而天下治矣。天地之间。事机万变。有动有息。有胜有复。所谓开阖也。吾处其间。无为事始。无为物先。而常守其静以待之。是则所谓为
静。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离。如人登车而常载于其上。则魂安静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长生久视之要诀也。愚谓魂者。阳之神也。魄者。阴之精也。神象火而常升。精涵水而恒降。其势不相离则不已。况人之生也。喜怒忧思情欲交炽。火之升也。无刻暂息。此皆所以速其离而日趋于死也。善卫生者。节精以完神。存气以抱精。使情不炎上。心不骛外。而灵明之体。常守吾方寸之中。则火既降水常升。真可以长生而久视也。此则参同契所谓三光陆沉。温养子珠。而后世修炼之家所指铅汞龙虎婴儿姹女者。皆即此水火之象而演之耳。气一乎内而不作乎外。此所谓致柔也。婴儿者。始生之孩。纯然乎无知无欲者也。玄览。未详。吴幼清曰。目有所见。则神驰于外。闭目藏视为玄。虽玄之中。犹有所览。是犹有疵也。故亦并涤除之也。夫抱一而无离。则神完矣。致柔而婴儿。则气和矣。涤览而无疵。则德全矣。有是三者而行之。以爱民之心。则无所作为而天下治矣。天地之间。事机万变。有动有息。有胜有复。所谓开阖也。吾处其间。无为事始。无为物先。而常守其静以待之。是则所谓为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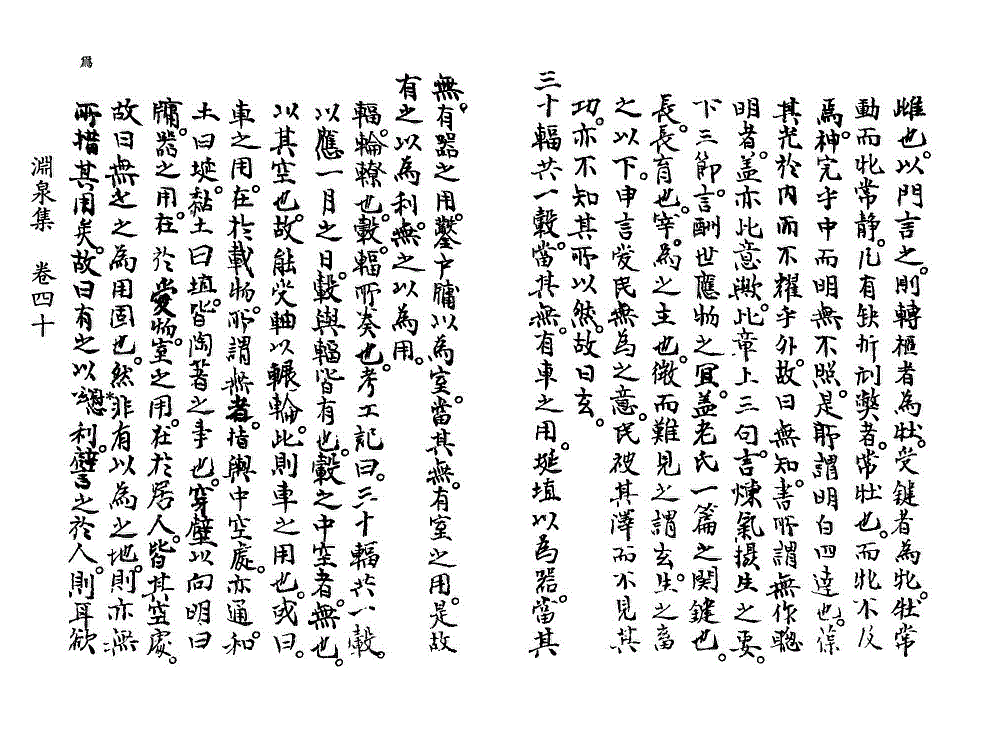 雌也。以门言之。则转枢者为牡。受键者为牝。牡常动而牝常静。凡有缺折刓弊者。常牡也。而牝不及焉。神完乎中而明无不照。是所谓明白四达也。葆其光于内而不耀乎外。故曰无知。书所谓无作聪明者。盖亦此意欤。此章上三句。言炼气摄生之要。下三节。言酬世应物之宜。盖老氏一篇之关键也。长。长育也。宰。为之主也。微而难见之谓玄。生之畜之以下。申言爱民无为之意。民被其泽而不见其功。亦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玄。
雌也。以门言之。则转枢者为牡。受键者为牝。牡常动而牝常静。凡有缺折刓弊者。常牡也。而牝不及焉。神完乎中而明无不照。是所谓明白四达也。葆其光于内而不耀乎外。故曰无知。书所谓无作聪明者。盖亦此意欤。此章上三句。言炼气摄生之要。下三节。言酬世应物之宜。盖老氏一篇之关键也。长。长育也。宰。为之主也。微而难见之谓玄。生之畜之以下。申言爱民无为之意。民被其泽而不见其功。亦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辐。轮轑也。毂。辐所奏也。考工记曰。三十辐共一毂。以应一月之日。毂与辐皆有也。毂之中空者。无也。以其空也。故能受轴以辗轮。此则车之用也。或曰。车之用。在于载物。所谓无者。指舆中空处。亦通。和土曰埏。黏土曰埴。皆陶著之事也。穿壁以向明曰牖。器之用。在于受物。室之用。在于居人。皆其空处。故曰无之之为用固也。然非有以为之地。则亦无所措其用矣。故曰有之以为利。譬之于人。则耳欲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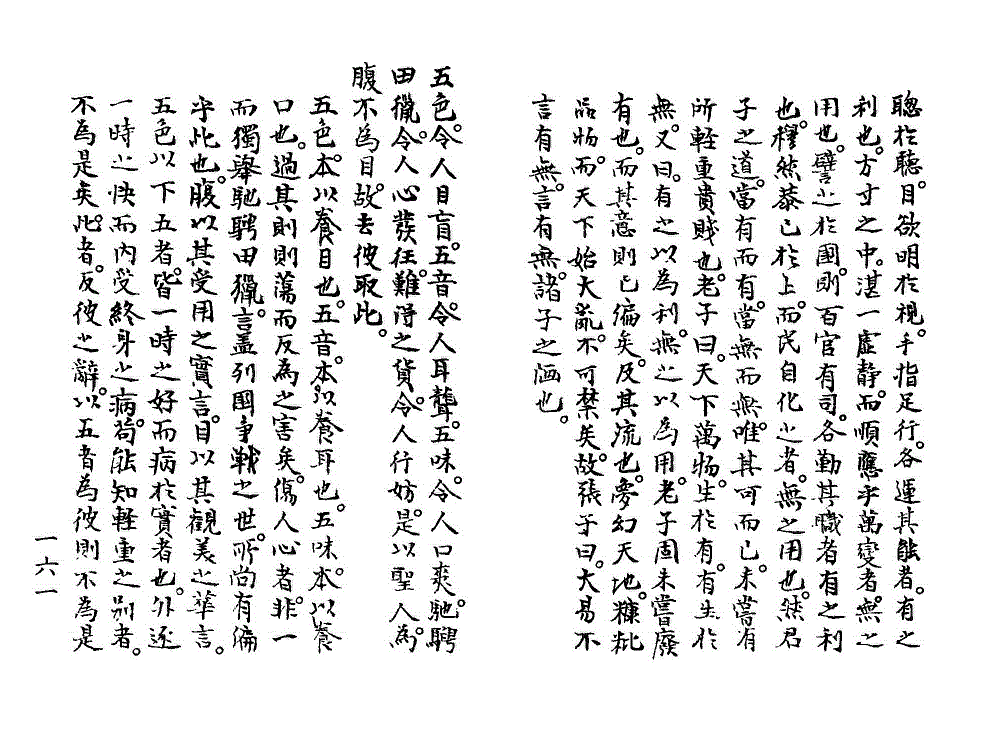 聪于听。目欲明于视。手指足行。各运其能者。有之利也。方寸之中。湛一虚静。而顺应乎万变者。无之用也。譬之于国。则百官有司。各勤其职者有之利也。穆然恭己于上。而民自化之者。无之用也。然君子之道。当有而有。当无而无。唯其可而已。未尝有所轻重贵贱也。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固未尝废有也。而其意则已偏矣。及其流也。梦幻天地。糠秕品物。而天下始大乱。不可禁矣。故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聪于听。目欲明于视。手指足行。各运其能者。有之利也。方寸之中。湛一虚静。而顺应乎万变者。无之用也。譬之于国。则百官有司。各勤其职者有之利也。穆然恭己于上。而民自化之者。无之用也。然君子之道。当有而有。当无而无。唯其可而已。未尝有所轻重贵贱也。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固未尝废有也。而其意则已偏矣。及其流也。梦幻天地。糠秕品物。而天下始大乱。不可禁矣。故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本以养目也。五音。本以养耳也。五味。本以养口也。过其则则荡而反为之害矣。伤人心者。非一而独举驰骋田猎。言盖列国争战之世。所尚有偏乎此也。腹以其受用之实言。目以其观美之华言。五色以下五者。皆一时之好而病于实者也。外逐一时之快而内受终身之病。苟能知轻重之别者。不为是矣。此者。反彼之辞。以五者为彼则不为是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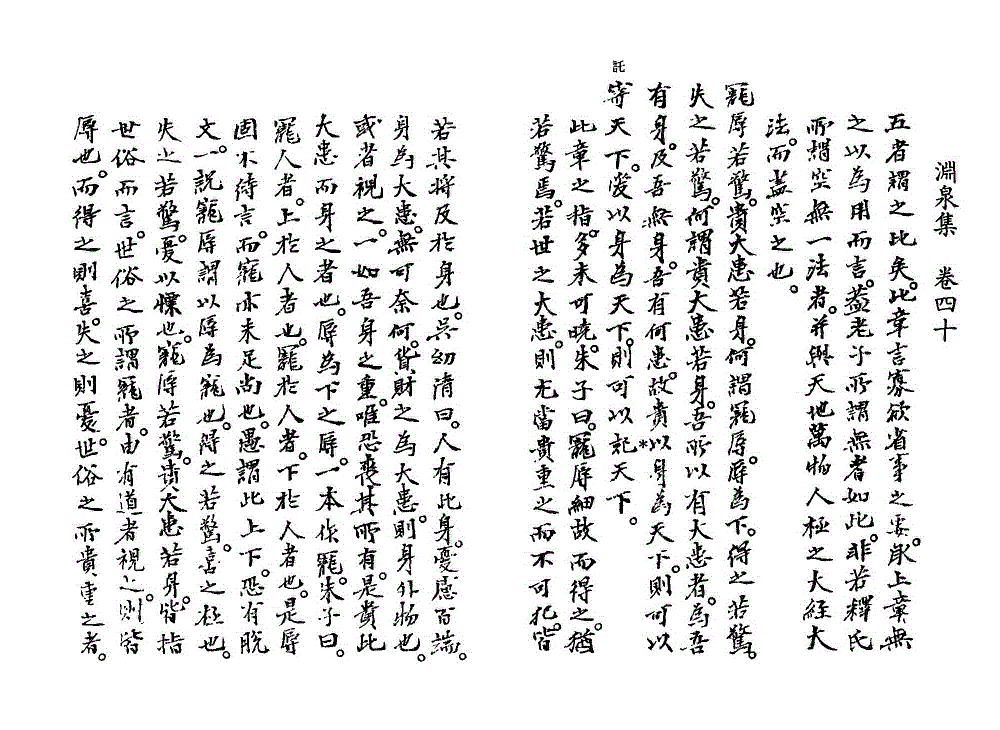 五者谓之此矣。此章言寡欲省事之要。承上章无之以为用而言。盖老子所谓无者如此。非若释氏所谓空无一法者。并与天地万物人极之大经大法。而尽空之也。
五者谓之此矣。此章言寡欲省事之要。承上章无之以为用而言。盖老子所谓无者如此。非若释氏所谓空无一法者。并与天地万物人极之大经大法。而尽空之也。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
此章之指。多未可晓。朱子曰。宠辱细故而得之。犹若惊焉。若世之大患。则尤当贵重之而不可犯。皆若其将及于身也。吴幼清曰。人有此身。忧虑百端。身为大患。无可奈何。货财之为大患。则身外物也。或者视之。一如吾身之重。唯恐丧其所有。是贵此大患而身之者也。辱为下之辱。一本作宠。朱子曰。宠人者。上于人者也。宠于人者。下于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宠亦未足尚也。愚谓此上下。恐有脱文。一说宠辱谓以辱为宠也。得之若惊。喜之极也。失之若惊。忧以慄也。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皆指世俗而言。世俗之所谓宠者。由有道者视之。则皆辱也。而得之则喜。失之则忧。世俗之所贵重之者。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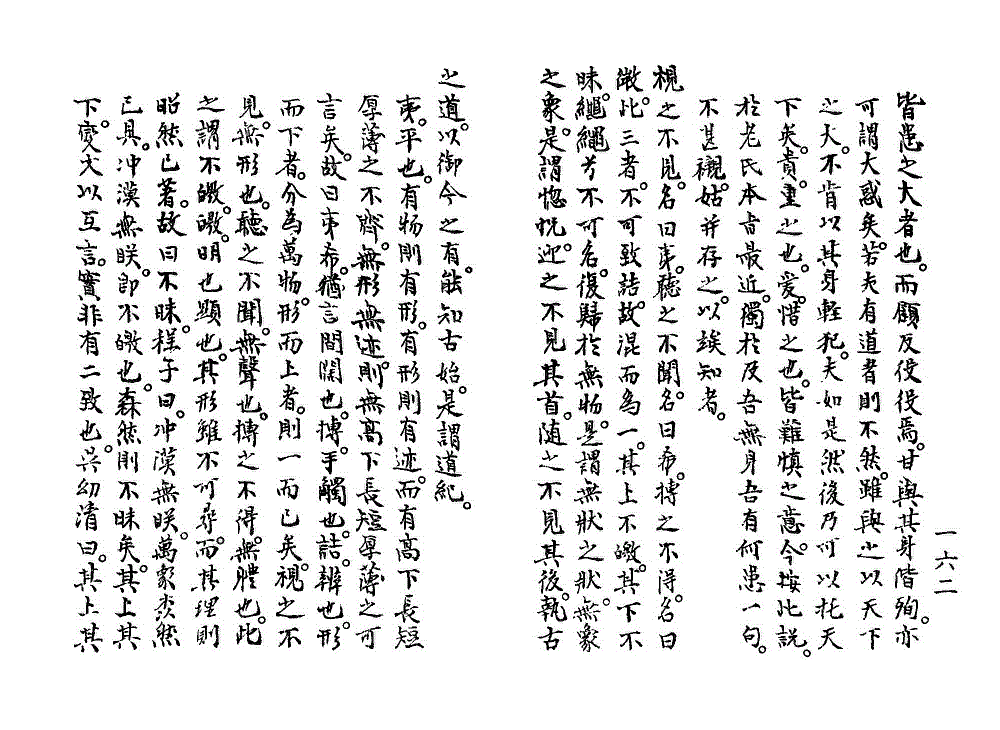 皆患之大者也。而顾反役役焉。甘与其身偕殉。亦可谓大惑矣。若夫有道者则不然。虽与之以天下之大。不肯以其身轻犯。夫如是然后乃可以托天下矣。贵。重之也。爱。惜之也。皆难慎之意。今按此说。于老氏本旨最近。独于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句。不甚衬。姑并存之。以俟知者。
皆患之大者也。而顾反役役焉。甘与其身偕殉。亦可谓大惑矣。若夫有道者则不然。虽与之以天下之大。不肯以其身轻犯。夫如是然后乃可以托天下矣。贵。重之也。爱。惜之也。皆难慎之意。今按此说。于老氏本旨最近。独于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句。不甚衬。姑并存之。以俟知者。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夷。平也。有物则有形。有形则有迹。而有高下长短厚薄之不齐。无形无迹。则无高下长短厚薄之可言矣。故曰夷希。犹言间阔也。搏。手触也。诘。辨也。形而下者。分为万物。形而上者。则一而已矣。视之不见。无形也。听之不闻。无声也。搏之不得。无体也。此之谓不皦。皦。明也显也。其形虽不可寻。而其理则昭然已著。故曰不昧。程子曰。冲漠无眹。万象森然已具。冲漠无眹。即不皦也。森然则不昧矣。其上其下。变文以互言。实非有二致也。吴幼清曰。其上其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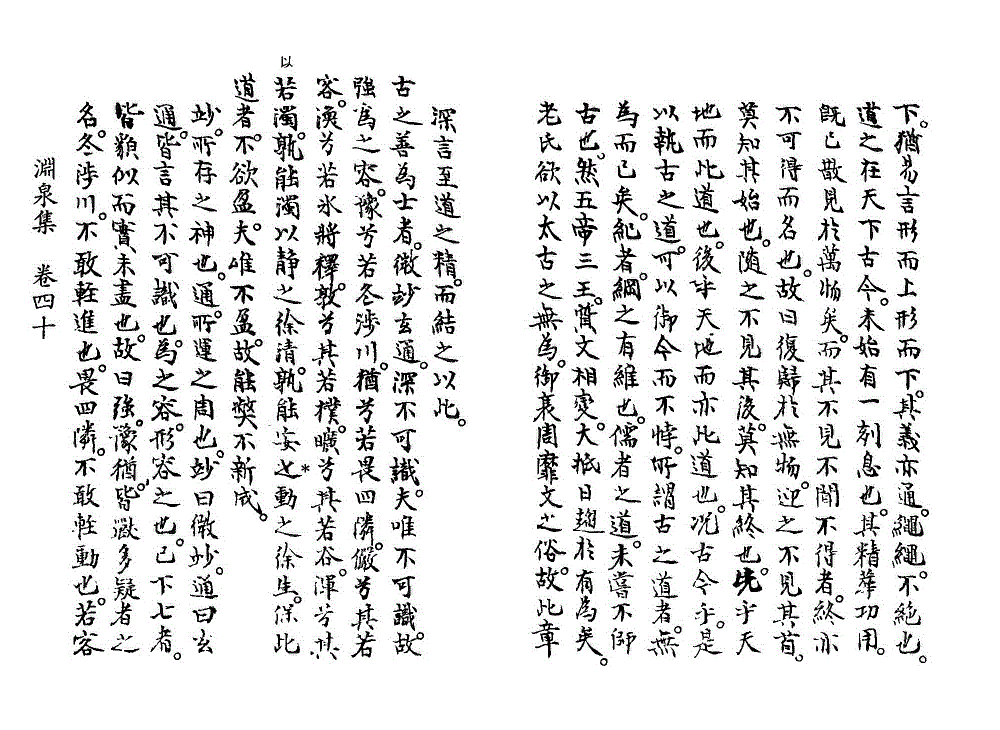 下。犹易言形而上形而下。其义亦通。绳绳。不绝也。道之在天下古今。未始有一刻息也。其精华功用。既已散见于万物矣。而其不见不闻不得者。终亦不可得而名也。故曰复归于无物。迎之不见其首。莫知其始也。随之不见其后。莫知其终也。先乎天地而此道也。后乎天地而亦此道也。况古今乎。是以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而不悖。所谓古之道者。无为而已矣。纪者。纲之有维也。儒者之道。未尝不师古也。然五帝三王。质文相变。大抵日趋于有为矣。老氏欲以太古之无为。御衰周靡文之俗。故此章深言至道之精。而结之以此。
下。犹易言形而上形而下。其义亦通。绳绳。不绝也。道之在天下古今。未始有一刻息也。其精华功用。既已散见于万物矣。而其不见不闻不得者。终亦不可得而名也。故曰复归于无物。迎之不见其首。莫知其始也。随之不见其后。莫知其终也。先乎天地而此道也。后乎天地而亦此道也。况古今乎。是以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而不悖。所谓古之道者。无为而已矣。纪者。纲之有维也。儒者之道。未尝不师古也。然五帝三王。质文相变。大抵日趋于有为矣。老氏欲以太古之无为。御衰周靡文之俗。故此章深言至道之精。而结之以此。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妙。所存之神也。通。所运之周也。妙曰微妙。通曰玄通。皆言其不可识也。为之容。形容之也。已下七者。皆貌似而实未尽也。故曰强。豫犹。皆兽多疑者之名。冬涉川。不敢轻进也。畏四邻。不敢轻动也。若客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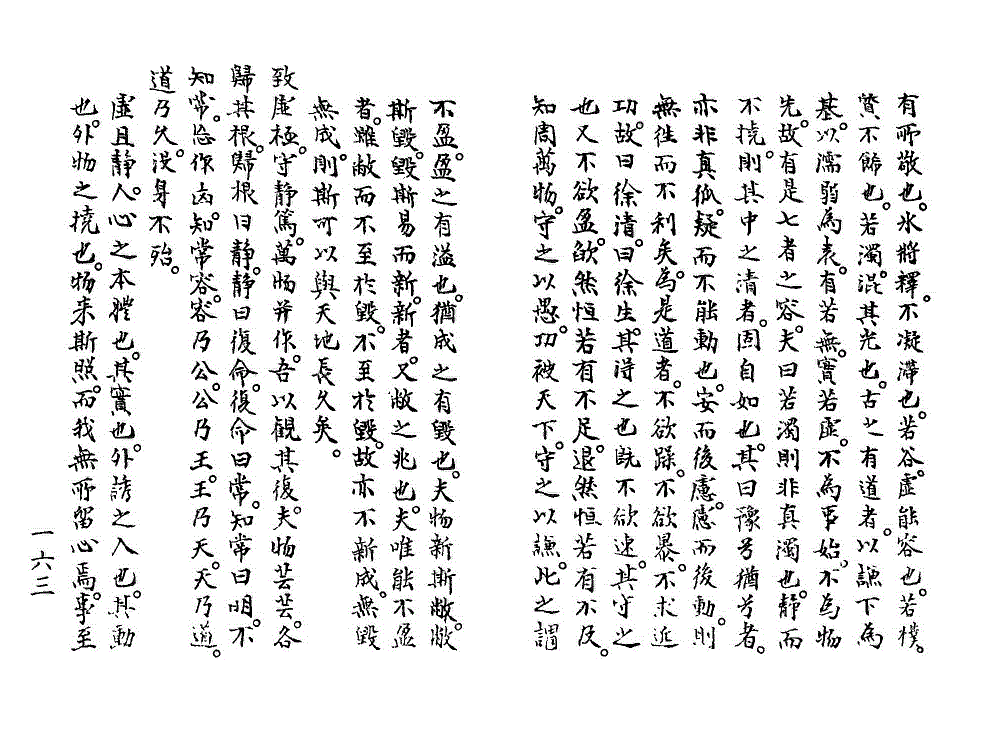 有所敬也。冰将释。不凝滞也。若谷。虚能容也。若朴。质不饰也。若浊。混其光也。古之有道者。以谦下为基。以濡弱为表。有若无。实若虚。不为事始。不为物先。故有是七者之容。夫曰若浊则非真浊也。静而不挠。则其中之清者。固自如也。其曰豫兮犹兮者。亦非真狐。疑而不能动也。安而后虑。虑而后动。则无往而不利矣。为是道者。不欲躁。不欲暴。不求近功。故曰徐清。曰徐生。其得之也既不欲速。其守之也又不欲盈。欿然恒若有不足。退然恒若有不及。知周万物。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谦。此之谓不盈。盈之有溢也。犹成之有毁也。夫物新斯敝。敝斯毁。毁斯易而新。新者。又敝之兆也。夫唯能不盈者。虽敝而不至于毁。不至于毁。故亦不新成。无毁无成。则斯可以与天地长久矣。
有所敬也。冰将释。不凝滞也。若谷。虚能容也。若朴。质不饰也。若浊。混其光也。古之有道者。以谦下为基。以濡弱为表。有若无。实若虚。不为事始。不为物先。故有是七者之容。夫曰若浊则非真浊也。静而不挠。则其中之清者。固自如也。其曰豫兮犹兮者。亦非真狐。疑而不能动也。安而后虑。虑而后动。则无往而不利矣。为是道者。不欲躁。不欲暴。不求近功。故曰徐清。曰徐生。其得之也既不欲速。其守之也又不欲盈。欿然恒若有不足。退然恒若有不及。知周万物。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谦。此之谓不盈。盈之有溢也。犹成之有毁也。夫物新斯敝。敝斯毁。毁斯易而新。新者。又敝之兆也。夫唯能不盈者。虽敝而不至于毁。不至于毁。故亦不新成。无毁无成。则斯可以与天地长久矣。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忘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虚且静。人心之本体也。其实也。外诱之入也。其动也。外物之挠也。物来斯照。而我无所留心焉。事至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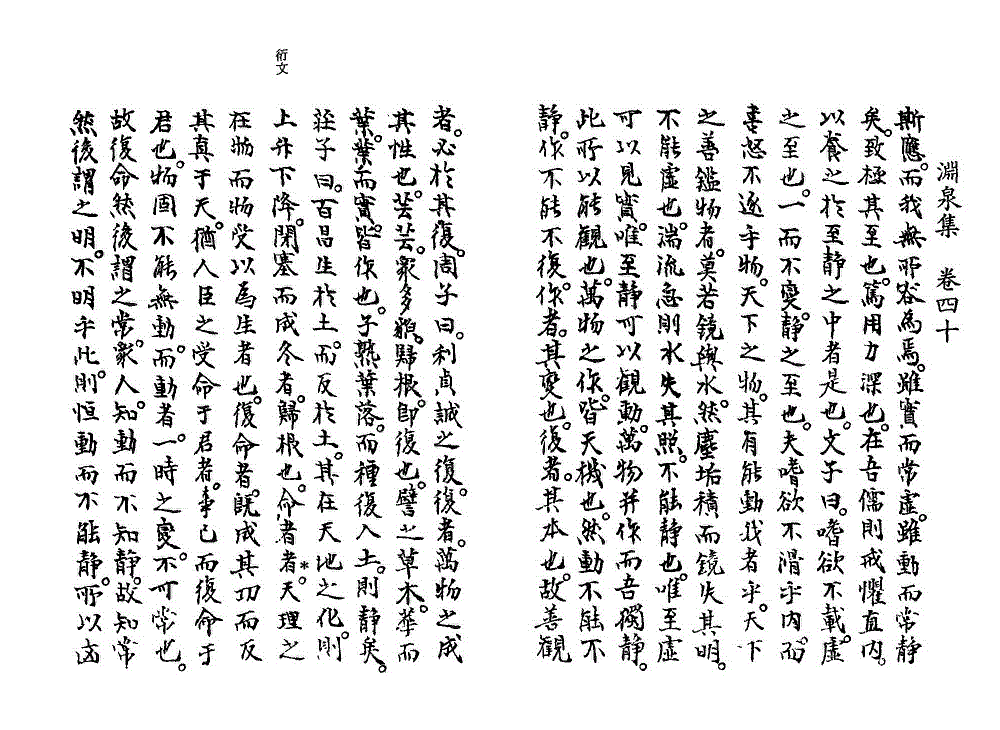 斯应。而我无所容为焉。虽实而常虚。虽动而常静矣。致极其至也。笃用力深也。在吾儒则戒惧直内。以养之于至静之中者是也。文子曰。嗜欲不载。虚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夫嗜欲不滑乎内。而喜怒不逐乎物。天下之物。其有能动我者乎。天下之善鉴物者。莫若镜与水。然尘垢积而镜失其明。不能虚也。湍流急则水失其照。不能静也。唯至虚可以见实。唯至静可以观动。万物并作而吾独静。此所以能观也。万物之作。皆天机也。然动不能不静。作不能不复。作者。其变也。复者。其本也。故善观者。必于其复。周子曰。利贞诚之复。复者。万物之成其性也。芸芸。众多貌。归根。即复也。譬之草木。华而叶。叶而实。皆作也。子熟叶落。而种复入土。则静矣。庄子曰。百昌生于土。而反于土。其在天地之化。则上升下降。闭塞而成冬者。归根也。命者。天理之在物而物受以为生者也。复命者。既成其功而反其真于天。犹人臣之受命于君者。事已而复命于君也。物固不能无动。而动者。一时之变。不可常也。故复命然后谓之常。众人。知动而不知静。故知常然后谓之明。不明乎此。则恒动而不能静。所以凶
斯应。而我无所容为焉。虽实而常虚。虽动而常静矣。致极其至也。笃用力深也。在吾儒则戒惧直内。以养之于至静之中者是也。文子曰。嗜欲不载。虚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夫嗜欲不滑乎内。而喜怒不逐乎物。天下之物。其有能动我者乎。天下之善鉴物者。莫若镜与水。然尘垢积而镜失其明。不能虚也。湍流急则水失其照。不能静也。唯至虚可以见实。唯至静可以观动。万物并作而吾独静。此所以能观也。万物之作。皆天机也。然动不能不静。作不能不复。作者。其变也。复者。其本也。故善观者。必于其复。周子曰。利贞诚之复。复者。万物之成其性也。芸芸。众多貌。归根。即复也。譬之草木。华而叶。叶而实。皆作也。子熟叶落。而种复入土。则静矣。庄子曰。百昌生于土。而反于土。其在天地之化。则上升下降。闭塞而成冬者。归根也。命者。天理之在物而物受以为生者也。复命者。既成其功而反其真于天。犹人臣之受命于君者。事已而复命于君也。物固不能无动。而动者。一时之变。不可常也。故复命然后谓之常。众人。知动而不知静。故知常然后谓之明。不明乎此。则恒动而不能静。所以凶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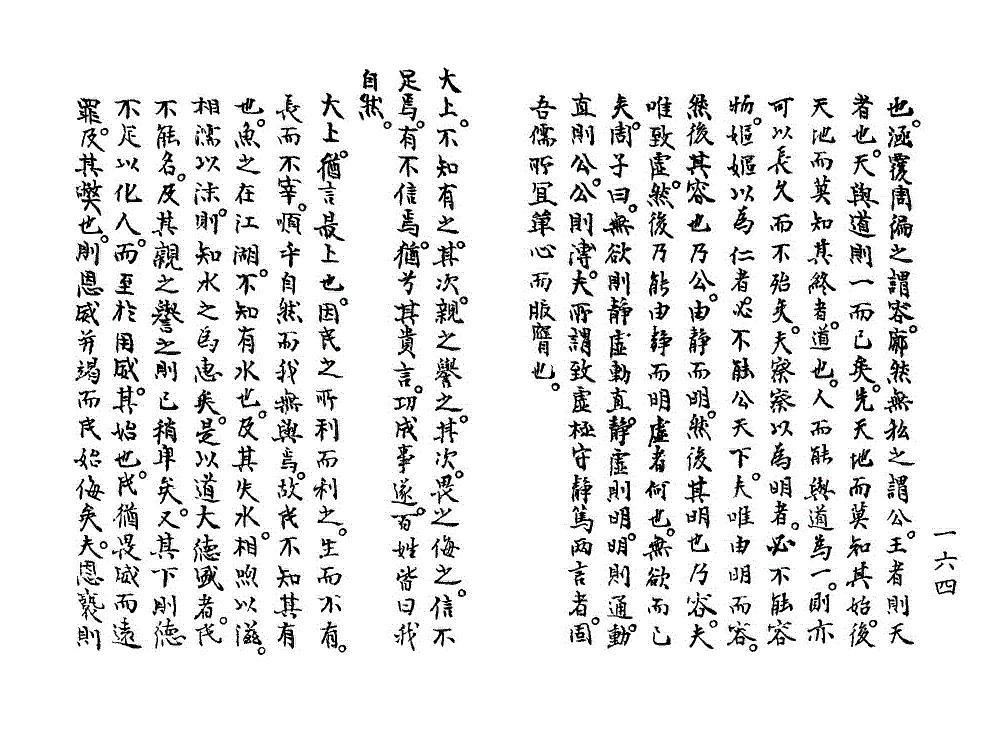 也。涵覆周遍之谓容。廓然无私之谓公。王者则天者也。天与道则一而已矣。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后天地而莫知其终者。道也。人而能与道为一。则亦可以长久而不殆矣。夫察察以为明者。必不能容物。妪妪以为仁者。必不能公天下。夫唯由明而容。然后其容也乃公。由静而明。然后其明也乃容。夫唯致虚。然后乃能由静而明虚者何也。无欲而已矣。周子曰。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夫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两言者。固吾儒所宜单心而服膺也。
也。涵覆周遍之谓容。廓然无私之谓公。王者则天者也。天与道则一而已矣。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后天地而莫知其终者。道也。人而能与道为一。则亦可以长久而不殆矣。夫察察以为明者。必不能容物。妪妪以为仁者。必不能公天下。夫唯由明而容。然后其容也乃公。由静而明。然后其明也乃容。夫唯致虚。然后乃能由静而明虚者何也。无欲而已矣。周子曰。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夫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两言者。固吾儒所宜单心而服膺也。大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大上。犹言最上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生而不有。长而不宰。顺乎自然而我无与焉。故民不知其有也。鱼之在江湖。不知有水也。及其失水。相喣以滋。相濡以沫。则知水之为惠矣。是以道大德盛者。民不能名。及其亲之誉之则已稍卑矣。又其下则德不足以化人。而至于用威。其始也。民犹畏威而远罪。及其弊也。则恩威并竭而民始侮矣。夫恩亵则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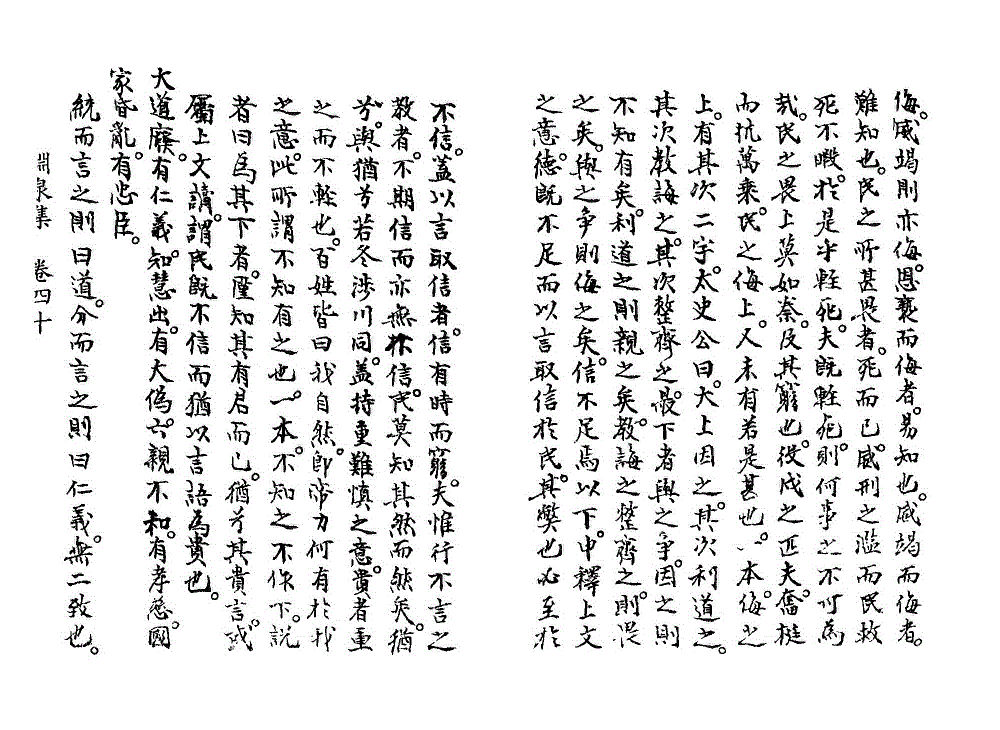 侮。威竭则亦侮。恩亵而侮者。易知也。威竭而侮者。难知也。民之所甚畏者。死而已。威刑之滥而民救死不暇。于是乎轻死。夫既轻死。则何事之不可为哉。民之畏上莫如秦。及其穷也。役戍之匹夫。奋挺而抗万乘。民之侮上。又未有若是甚也。一本。侮之上。有其次二字。太史公曰。大上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则不知有矣。利道之则亲之矣。教诲之整齐之。则畏之矣。与之争则侮之矣。信不足焉以下。申释上文之意。德既不足而以言取信于民。其弊也必至于不信。盖以言取信者。信有时而穷。夫惟行不言之教者。不期信而亦无不信。民莫知其然而然矣。犹兮。与犹兮若冬涉川同。盖持重难慎之意。贵者重之而不轻也。百姓皆曰我自然。即帝力何有于我之意。此所谓不知有之也。一本。不知之不作下。说者曰为其下者。廑知其有君而已。犹兮其贵言。或属上文读。谓民既不信而犹以言语为贵也。
侮。威竭则亦侮。恩亵而侮者。易知也。威竭而侮者。难知也。民之所甚畏者。死而已。威刑之滥而民救死不暇。于是乎轻死。夫既轻死。则何事之不可为哉。民之畏上莫如秦。及其穷也。役戍之匹夫。奋挺而抗万乘。民之侮上。又未有若是甚也。一本。侮之上。有其次二字。太史公曰。大上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则不知有矣。利道之则亲之矣。教诲之整齐之。则畏之矣。与之争则侮之矣。信不足焉以下。申释上文之意。德既不足而以言取信于民。其弊也必至于不信。盖以言取信者。信有时而穷。夫惟行不言之教者。不期信而亦无不信。民莫知其然而然矣。犹兮。与犹兮若冬涉川同。盖持重难慎之意。贵者重之而不轻也。百姓皆曰我自然。即帝力何有于我之意。此所谓不知有之也。一本。不知之不作下。说者曰为其下者。廑知其有君而已。犹兮其贵言。或属上文读。谓民既不信而犹以言语为贵也。大道废。有仁义。知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统而言之则曰道。分而言之则曰仁义。无二致也。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5L 页
 老子病世之沽惠以为仁。矜侠以为义也。故并与圣人之言仁义也而抑之。其意则有激云尔。其言则不可以训矣。知慧所以防伪也。知慧出而伪益滋。庄子曰。为之符玺斗斛权衡。则并与符玺斗斛权衡而窃之。盖此意也。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天下之为父者无不慈。天下之为子者无不孝。则无孝慈之名。君明于上。民顺于下。则无忠臣之名。黄帝尧汤。非不能尽伦也。而舜独有孝之名。皋卨夷龙。非不能事君也。而关龙逄独以忠称。故有孝子忠臣之名者。国家之不幸也。老子生于衰季。嫉夫人之尚贤而标名也。故其言如此。然不能禁六亲之不和国家之昏乱。而先恶夫孝子忠臣之名。其弊也又将不知所底止。唯所谓知慧出。有大伪者。则格言也。夫亿兆之奸欺。非一人之所能尽防也。故圣人之居人上也。推至诚而任之。廓大公而御之。天下归德而奸自无所容。彼欲以私知小慧。沾沾以为察者。固足以滋伪而已矣。
老子病世之沽惠以为仁。矜侠以为义也。故并与圣人之言仁义也而抑之。其意则有激云尔。其言则不可以训矣。知慧所以防伪也。知慧出而伪益滋。庄子曰。为之符玺斗斛权衡。则并与符玺斗斛权衡而窃之。盖此意也。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天下之为父者无不慈。天下之为子者无不孝。则无孝慈之名。君明于上。民顺于下。则无忠臣之名。黄帝尧汤。非不能尽伦也。而舜独有孝之名。皋卨夷龙。非不能事君也。而关龙逄独以忠称。故有孝子忠臣之名者。国家之不幸也。老子生于衰季。嫉夫人之尚贤而标名也。故其言如此。然不能禁六亲之不和国家之昏乱。而先恶夫孝子忠臣之名。其弊也又将不知所底止。唯所谓知慧出。有大伪者。则格言也。夫亿兆之奸欺。非一人之所能尽防也。故圣人之居人上也。推至诚而任之。廓大公而御之。天下归德而奸自无所容。彼欲以私知小慧。沾沾以为察者。固足以滋伪而已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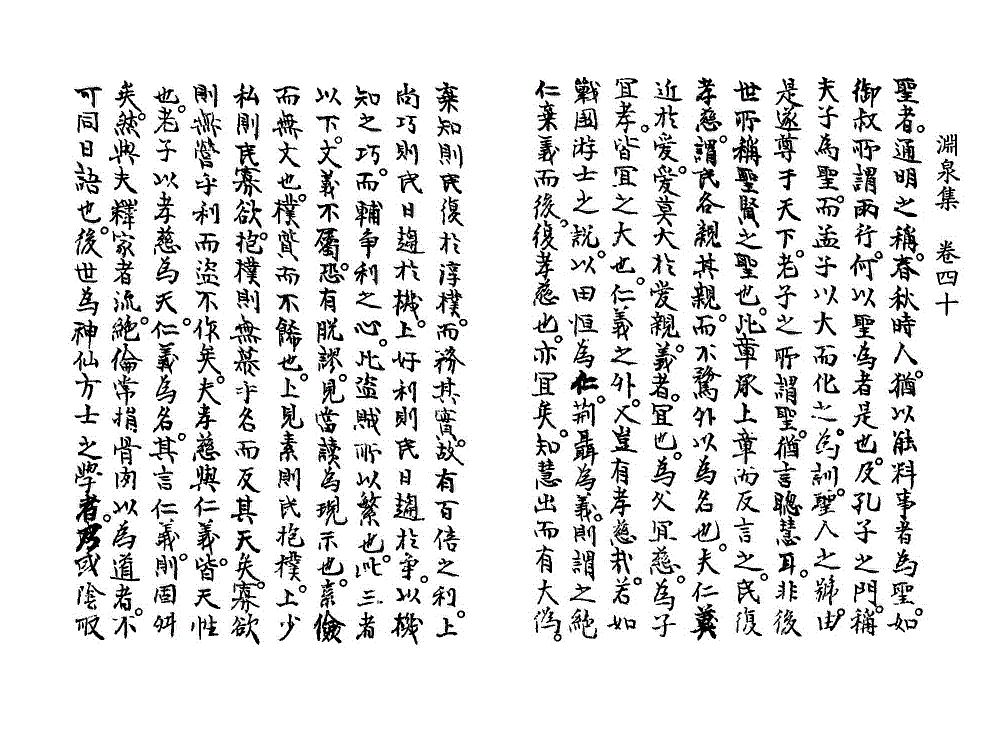 圣者。通明之称。春秋时人。犹以能料事者为圣。如御叔所谓两行。何以圣为者是也。及孔子之门。称夫子为圣。而孟子以大而化之。为训。圣人之号。由是遂尊于天下。老子之所谓圣。犹言聪慧耳。非后世所称圣贤之圣也。此章承上章而反言之。民复孝慈。谓民各亲其亲。而不骛外以为名也。夫仁莫近于爱。爱莫大于爱亲。义者。宜也。为父宜慈。为子宜孝。皆宜之大也。仁义之外。又岂有孝慈哉。若如战国游士之说。以田恒为仁。荆聂为义。则谓之绝仁弃义而后。复孝慈也。亦宜矣。知慧出而有大伪。弃知则民复于淳朴。而务其实。故有百倍之利。上尚巧则民日趋于机。上好利则民日趋于争。以机知之巧。而辅争利之心。此盗贼所以繁也。此三者以下。文义不属。恐有脱谬。见当读为现示也。素俭而无文也。朴质而不饰也。上见素则民抱朴。上少私则民寡欲。抱朴则无慕乎名而反其天矣。寡欲则无营乎利而盗不作矣。夫孝慈与仁义。皆天性也。老子以孝慈为天。仁义为名。其言仁义。则固舛矣。然与夫释家者流。绝伦常捐骨肉以为道者。不可同日语也。后世为神仙方士之学者。乃或阴取
圣者。通明之称。春秋时人。犹以能料事者为圣。如御叔所谓两行。何以圣为者是也。及孔子之门。称夫子为圣。而孟子以大而化之。为训。圣人之号。由是遂尊于天下。老子之所谓圣。犹言聪慧耳。非后世所称圣贤之圣也。此章承上章而反言之。民复孝慈。谓民各亲其亲。而不骛外以为名也。夫仁莫近于爱。爱莫大于爱亲。义者。宜也。为父宜慈。为子宜孝。皆宜之大也。仁义之外。又岂有孝慈哉。若如战国游士之说。以田恒为仁。荆聂为义。则谓之绝仁弃义而后。复孝慈也。亦宜矣。知慧出而有大伪。弃知则民复于淳朴。而务其实。故有百倍之利。上尚巧则民日趋于机。上好利则民日趋于争。以机知之巧。而辅争利之心。此盗贼所以繁也。此三者以下。文义不属。恐有脱谬。见当读为现示也。素俭而无文也。朴质而不饰也。上见素则民抱朴。上少私则民寡欲。抱朴则无慕乎名而反其天矣。寡欲则无营乎利而盗不作矣。夫孝慈与仁义。皆天性也。老子以孝慈为天。仁义为名。其言仁义。则固舛矣。然与夫释家者流。绝伦常捐骨肉以为道者。不可同日语也。后世为神仙方士之学者。乃或阴取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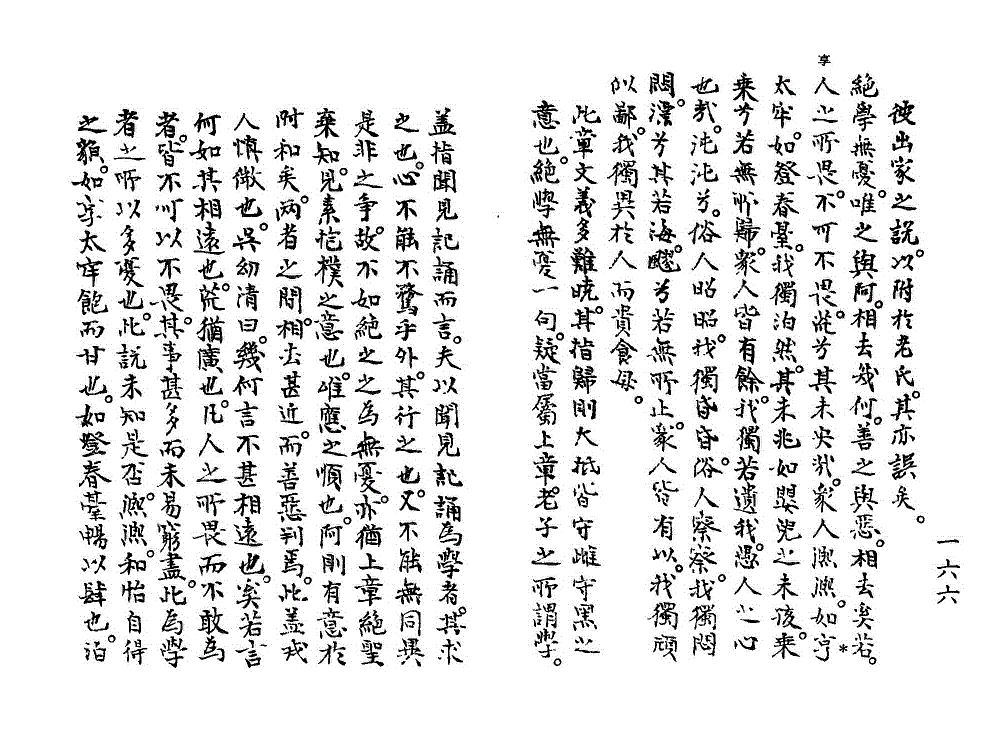 彼出家之说。以附于老氏。其亦误矣。
彼出家之说。以附于老氏。其亦误矣。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奚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然。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漂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此章文义多难晓。其指归则大抵皆守雌守黑之意也。绝学无忧一句。疑当属上章。老子之所谓学。盖指闻见记诵而言。夫以闻见记诵为学者。其求之也。心不能不骛乎外。其行之也。又不能无同异是非之争。故不如绝之之为无忧。亦犹上章绝圣弃知。见素抱朴之意也。唯应之顺也。阿则有意于附和矣。两者之间。相去甚近。而善恶判焉。此盖戒人慎微也。吴幼清曰。几何言不甚相远也。奚若言何如其相远也。荒犹广也。凡人之所畏而不敢为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穷尽。此为学者之所以多忧也。此说未知是否。熙熙。和怡自得之貌。如享太牢饱而甘也。如登春台畅以肆也。泊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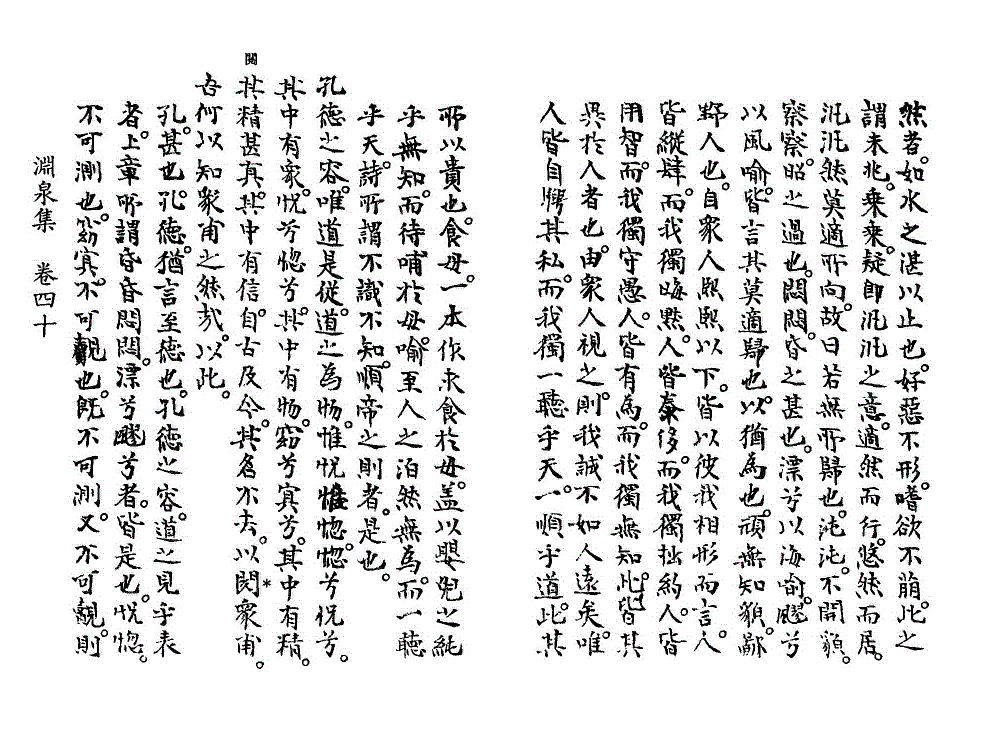 然者。如水之湛以止也。好恶不形。嗜欲不萌。此之谓未兆。乘乘。疑即汎汎之意。适然而行。悠然而居。汎汎然莫适所向。故曰若无所归也。沌沌。不开貌。察察。昭之过也。闷闷。昏之甚也。漂兮以海喻。飂兮以风喻。皆言其莫适归也。以犹为也。顽无知貌。鄙野人也。自众人熙熙以下。皆以彼我相形而言。人皆纵肆。而我独晦默。人皆泰侈。而我独拙约。人皆用智。而我独守愚。人皆有为。而我独无知。此皆其异于人者也。由众人视之。则我诚不如人远矣。唯人皆自骋其私。而我独一听乎天。一顺乎道。此其所以贵也。食母。一本作求食于母。盖以婴儿之纯乎无知。而待哺于母。喻至人之泊然无为。而一听乎天。诗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是也。
然者。如水之湛以止也。好恶不形。嗜欲不萌。此之谓未兆。乘乘。疑即汎汎之意。适然而行。悠然而居。汎汎然莫适所向。故曰若无所归也。沌沌。不开貌。察察。昭之过也。闷闷。昏之甚也。漂兮以海喻。飂兮以风喻。皆言其莫适归也。以犹为也。顽无知貌。鄙野人也。自众人熙熙以下。皆以彼我相形而言。人皆纵肆。而我独晦默。人皆泰侈。而我独拙约。人皆用智。而我独守愚。人皆有为。而我独无知。此皆其异于人者也。由众人视之。则我诚不如人远矣。唯人皆自骋其私。而我独一听乎天。一顺乎道。此其所以贵也。食母。一本作求食于母。盖以婴儿之纯乎无知。而待哺于母。喻至人之泊然无为。而一听乎天。诗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是也。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孔。甚也。孔德。犹言至德也。孔德之容。道之见乎表者。上章所谓昏昏闷闷。漂兮飂兮者。皆是也。恍惚。不可测也。窈冥。不可觌也。既不可测。又不可觌。则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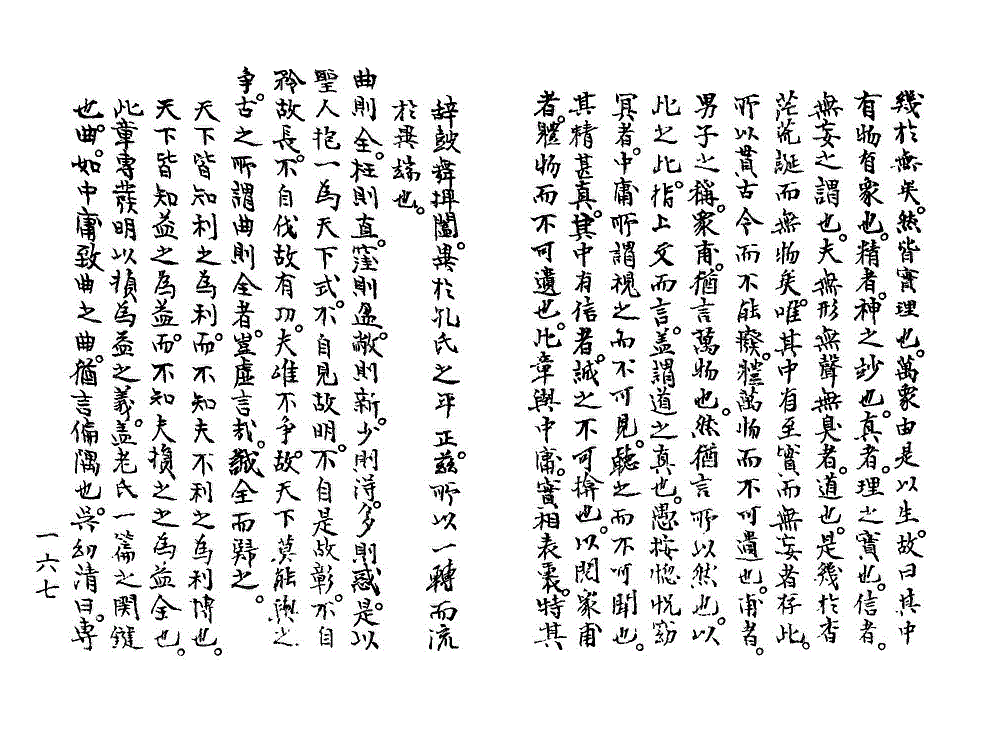 几于无矣。然皆实理也。万象由是以生。故曰其中有物有象也。精者。神之妙也。真者。理之实也。信者。无妄之谓也。夫无形无声无臭者。道也。是几于杳茫荒诞而无物矣。唯其中有至实而无妄者存此。所以贯古今而不能癈。体万物而不可遗也。甫者。男子之称。众甫。犹言万物也。然犹言所以然也。以此之此。指上文而言。盖谓道之真也。愚按惚恍窈冥者。中庸所谓视之而不可见。听之而不可闻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诚之不可掩也。以阅众甫者。体物而不可遗也。此章与中庸。实相表里。特其辞鼓舞捭阖。异于孔氏之平正。玆所以一转而流于异端也。
几于无矣。然皆实理也。万象由是以生。故曰其中有物有象也。精者。神之妙也。真者。理之实也。信者。无妄之谓也。夫无形无声无臭者。道也。是几于杳茫荒诞而无物矣。唯其中有至实而无妄者存此。所以贯古今而不能癈。体万物而不可遗也。甫者。男子之称。众甫。犹言万物也。然犹言所以然也。以此之此。指上文而言。盖谓道之真也。愚按惚恍窈冥者。中庸所谓视之而不可见。听之而不可闻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诚之不可掩也。以阅众甫者。体物而不可遗也。此章与中庸。实相表里。特其辞鼓舞捭阖。异于孔氏之平正。玆所以一转而流于异端也。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矜故长。不自伐故有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天下皆知利之为利。而不知夫不利之为利博也。天下皆知益之为益。而不知夫损之之为益全也。此章专发明以损为益之义。盖老氏一篇之关键也。曲。如中庸致曲之曲。犹言偏隅也。吴幼清曰。专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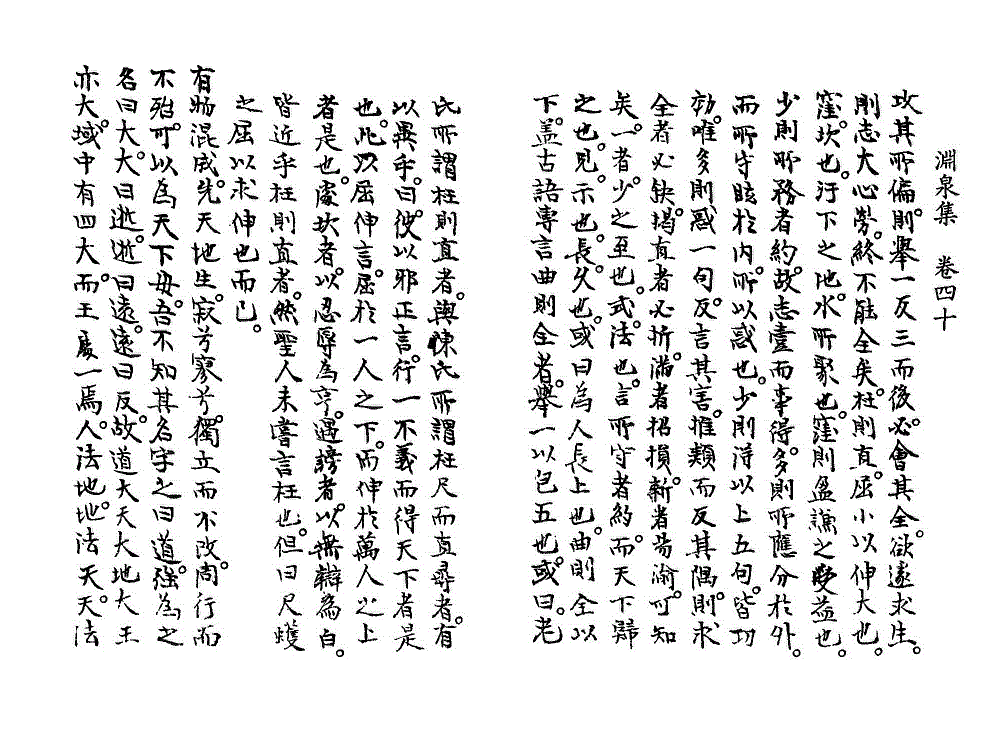 攻其所偏。则举一反三而后。必会其全。欲遽求生。则志大心劳。终不能全矣。杜则直。屈小以伸大也。洼。坎也。污下之池。水所聚也。洼则盈谦之受益也。少则所务者约。故志壹而事得。多则所应分于外。而所守眩于内。所以惑也。少则得以上五句。皆功效。唯多则惑一句。反言其害。推类而反其隅。则求全者必缺。揭直者必折。满者招损。新者易渝。可知矣。一者。少之至也。式。法也。言所守者约。而天下归之也。见。示也。长。久也。或曰为人长上也。曲则全以下。盖古语专言曲则全者。举一以包五也。或曰。老氏所谓枉则直者。与陈氏所谓枉尺而直寻者。有以异乎。曰。彼以邪正言。行一不义而得天下者是也。此以屈伸言。屈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者是也。处坎者。以忍辱为亨。遇谤者。以无辩为白。皆近乎枉则直者。然圣人未尝言枉也。但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而已。
攻其所偏。则举一反三而后。必会其全。欲遽求生。则志大心劳。终不能全矣。杜则直。屈小以伸大也。洼。坎也。污下之池。水所聚也。洼则盈谦之受益也。少则所务者约。故志壹而事得。多则所应分于外。而所守眩于内。所以惑也。少则得以上五句。皆功效。唯多则惑一句。反言其害。推类而反其隅。则求全者必缺。揭直者必折。满者招损。新者易渝。可知矣。一者。少之至也。式。法也。言所守者约。而天下归之也。见。示也。长。久也。或曰为人长上也。曲则全以下。盖古语专言曲则全者。举一以包五也。或曰。老氏所谓枉则直者。与陈氏所谓枉尺而直寻者。有以异乎。曰。彼以邪正言。行一不义而得天下者是也。此以屈伸言。屈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者是也。处坎者。以忍辱为亨。遇谤者。以无辩为白。皆近乎枉则直者。然圣人未尝言枉也。但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而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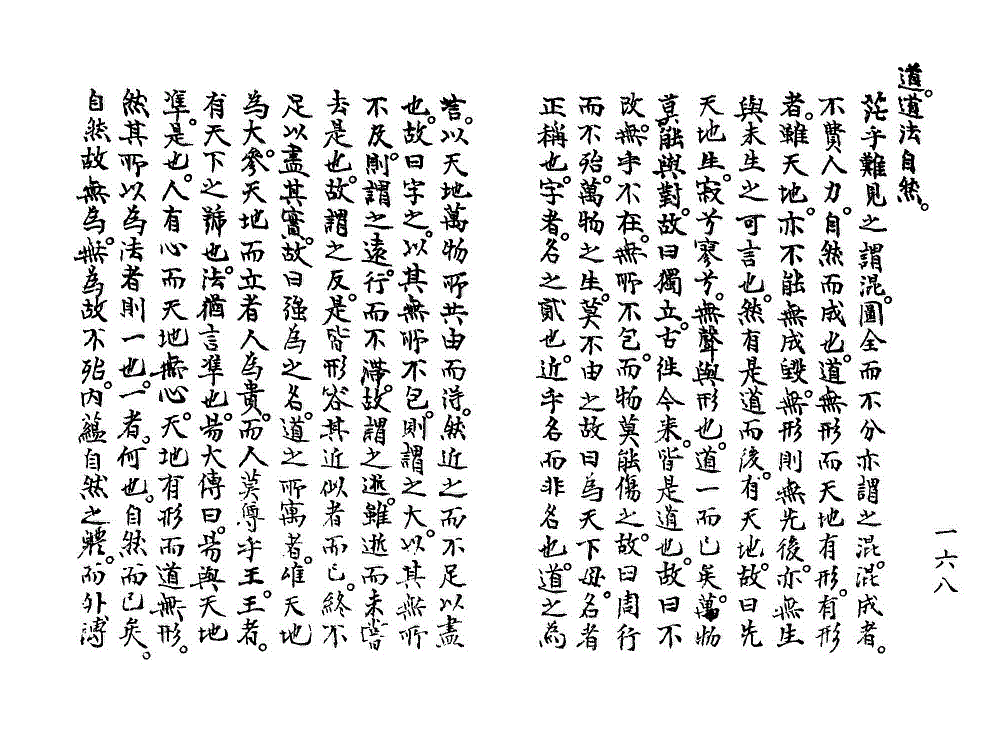 道。道法自然。
道。道法自然。茫乎难见之谓混。圆全而不分亦谓之混。混成者。不费人力。自然而成也。道无形而天地有形。有形者。虽天地。亦不能无成毁。无形则无先后。亦无生与未生之可言也。然有是道而后。有天地。故曰先天地生。寂兮寥兮。无声与形也。道一而已矣。万物莫能与对。故曰独立。古往今来。皆是道也。故曰不改。无乎不在。无所不包。而物莫能伤之。故曰周行而不殆。万物之生。莫不由之故曰为天下母。名者正称也。字者。名之贰也。近乎名而非名也。道之为言。以天地万物所共由而得。然近之而不足以尽也。故曰字之。以其无所不包。则谓之大。以其无所不及。则谓之远。行而不滞。故谓之逝。虽逝而未尝去是也。故谓之反。是皆形容其近似者而已。终不足以尽其实。故曰强为之名。道之所寓者。唯天地为大。参天地而立者人为贵。而人莫尊乎王。王者。有天下之号也。法犹言准也。易大传曰。易与天地准。是也。人有心而天地无心。天地有形而道无形。然其所以为法者则一也。一者。何也。自然而已矣。自然故无为。无为故不殆。内蕴自然之体。而外溥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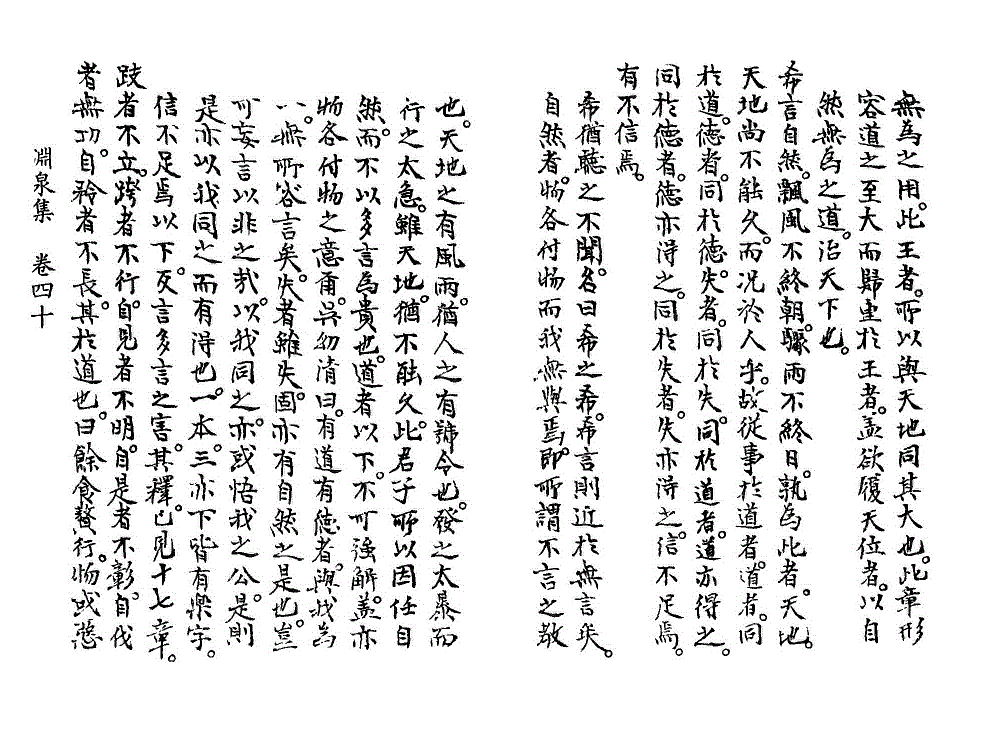 无为之用。此王者。所以与天地同其大也。此章形容道之至大而归重于王者。盖欲履天位者。以自然无为之道。治天下也。
无为之用。此王者。所以与天地同其大也。此章形容道之至大而归重于王者。盖欲履天位者。以自然无为之道。治天下也。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希犹听之不闻。名曰希之希。希言则近于无言矣。自然者。物各付物而我无与焉。即所谓不言之教也。天地之有风雨。犹人之有号令也。发之太暴而行之太急。虽天地。犹不能久。此君子所以因任自然。而不以多言为贵也。道者以下。不可强解。盖亦物各付物之意尔。吴幼清曰。有道有德者。与我为一。无所容言矣。失者虽失。固亦有自然之是也。岂可妄言以非之哉。以我同之。亦或悟我之公。是则是亦以我同之而有得也。一本。三亦下皆有乐字。信不足焉以下。反言多言之害。其释。已见十七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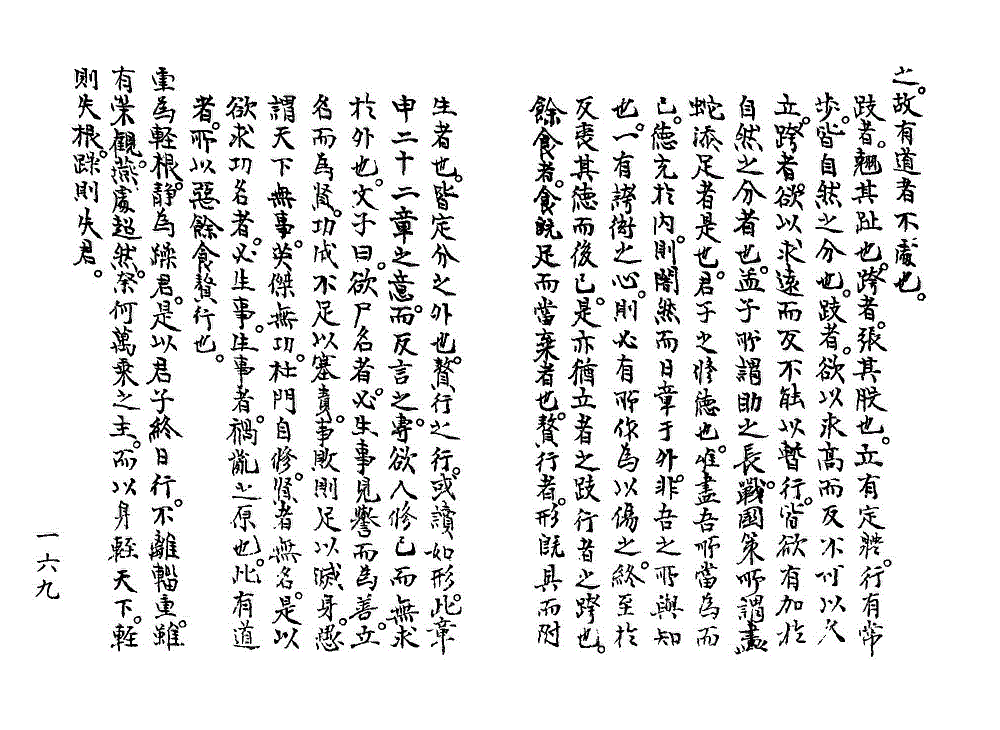 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之。故有道者不处也。跂者。翘其趾也。跨者。张其股也。立有定体。行有常步。皆自然之分也。跂者。欲以求高而反不可以久立。跨者。欲以求远而反不能以暂行。皆欲有加于自然之分者也。孟子所谓助之长。战国策所谓画蛇添足者是也。君子之修德也。唯尽吾所当为而已。德充于内。则闇然而日章于外。非吾之所与知也。一有誇衒之心。则必有所作为以伤之。终至于反丧其德而后已。是亦犹立者之跂行者之跨也。馀食者。食既足而当弃者也。赘行者。形既具而附生者也。皆定分之外也。赘行之行。或读如形。此章申二十二章之意。而反言之。专欲人修己而无求于外也。文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见誉而为善。立名而为贤。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则足以灭身。愚谓天下无事。英杰无功。杜门自修。贤者无名。是以欲求功名者。必生事。生事者。祸乱之原也。此有道者。所以恶馀食赘行也。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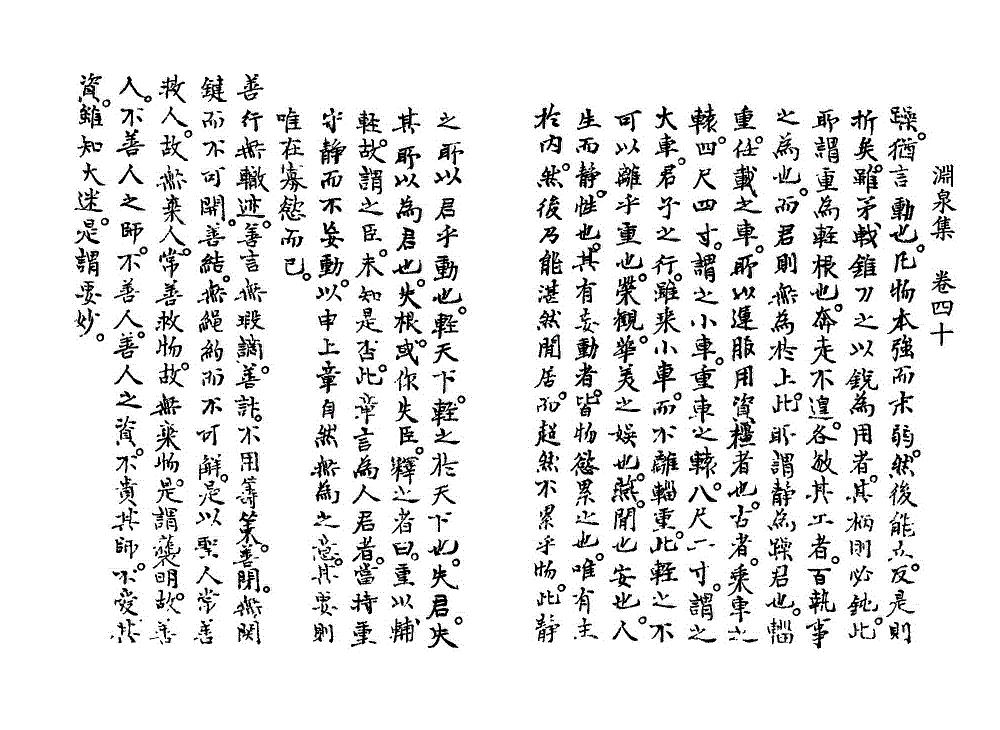 躁。犹言动也。凡物本强而末弱。然后能立。反是则折矣。虽矛戟锥刀之以锐为用者。其柄则必钝。此所谓重为轻根也。奔走不遑。各敏其工者。百执事之为也。而君则无为于上。此所谓静为躁君也。辎重。任载之车。所以运服用资
躁。犹言动也。凡物本强而末弱。然后能立。反是则折矣。虽矛戟锥刀之以锐为用者。其柄则必钝。此所谓重为轻根也。奔走不遑。各敏其工者。百执事之为也。而君则无为于上。此所谓静为躁君也。辎重。任载之车。所以运服用资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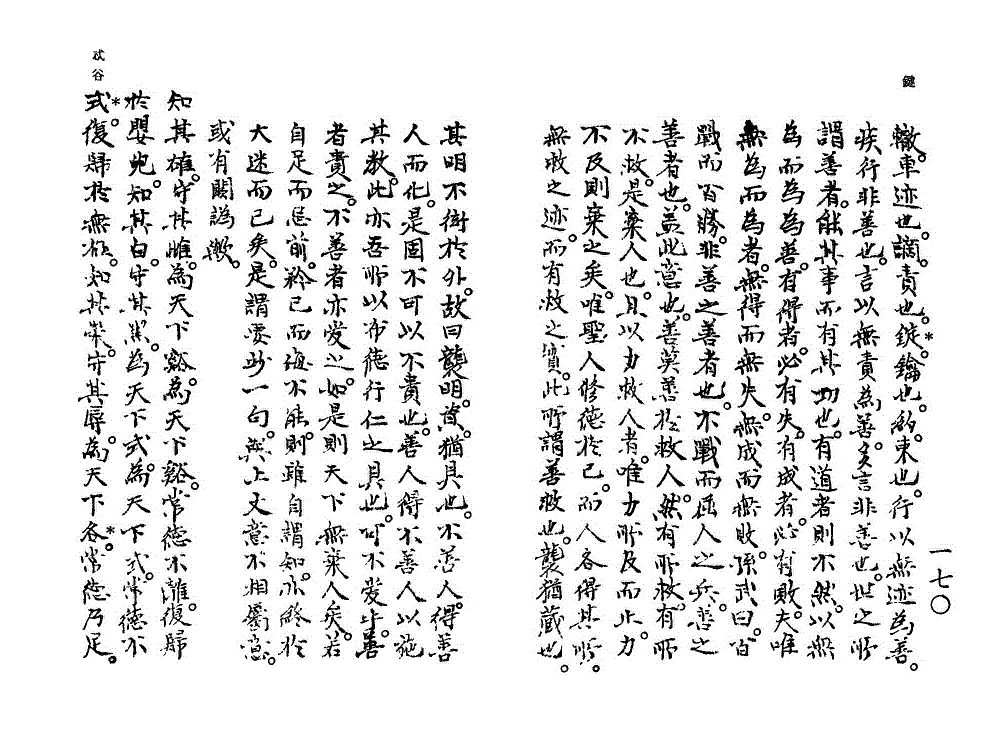 辙。车迹也。谪。责也。键。钥也。约。束也。行以无迹为善。疾行非善也。言以无责为善。多言非善也。世之所谓善者。能其事而有其功也。有道者则不然。以无为而为为善。有得者。必有失。有成者。必有败。夫唯无为而为者。无得而无失。无成而无败。孙武曰。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盖此意也。善莫善于救人。然有所救。有所不救。是弃人也。且以力救人者。唯力所及而止。力不及则弃之矣。唯圣人修德于己。而人各得其所。无救之迹。而有救之实。此所谓善救也。袭犹藏也。其明不衒于外。故曰袭明。资。犹具也。不善人。得善人而化。是固不可以不贵也。善人得不善人以施其教。此亦吾所以布德行仁之具也。可不爱乎。善者贵之。不善者亦爱之。如是则天下无弃人矣。若自足而忘前。矜己而侮不能。则虽自谓知。亦终于大迷而已矣。是谓要妙一句。与上文意不相属意。或有阙讹欤。
辙。车迹也。谪。责也。键。钥也。约。束也。行以无迹为善。疾行非善也。言以无责为善。多言非善也。世之所谓善者。能其事而有其功也。有道者则不然。以无为而为为善。有得者。必有失。有成者。必有败。夫唯无为而为者。无得而无失。无成而无败。孙武曰。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盖此意也。善莫善于救人。然有所救。有所不救。是弃人也。且以力救人者。唯力所及而止。力不及则弃之矣。唯圣人修德于己。而人各得其所。无救之迹。而有救之实。此所谓善救也。袭犹藏也。其明不衒于外。故曰袭明。资。犹具也。不善人。得善人而化。是固不可以不贵也。善人得不善人以施其教。此亦吾所以布德行仁之具也。可不爱乎。善者贵之。不善者亦爱之。如是则天下无弃人矣。若自足而忘前。矜己而侮不能。则虽自谓知。亦终于大迷而已矣。是谓要妙一句。与上文意不相属意。或有阙讹欤。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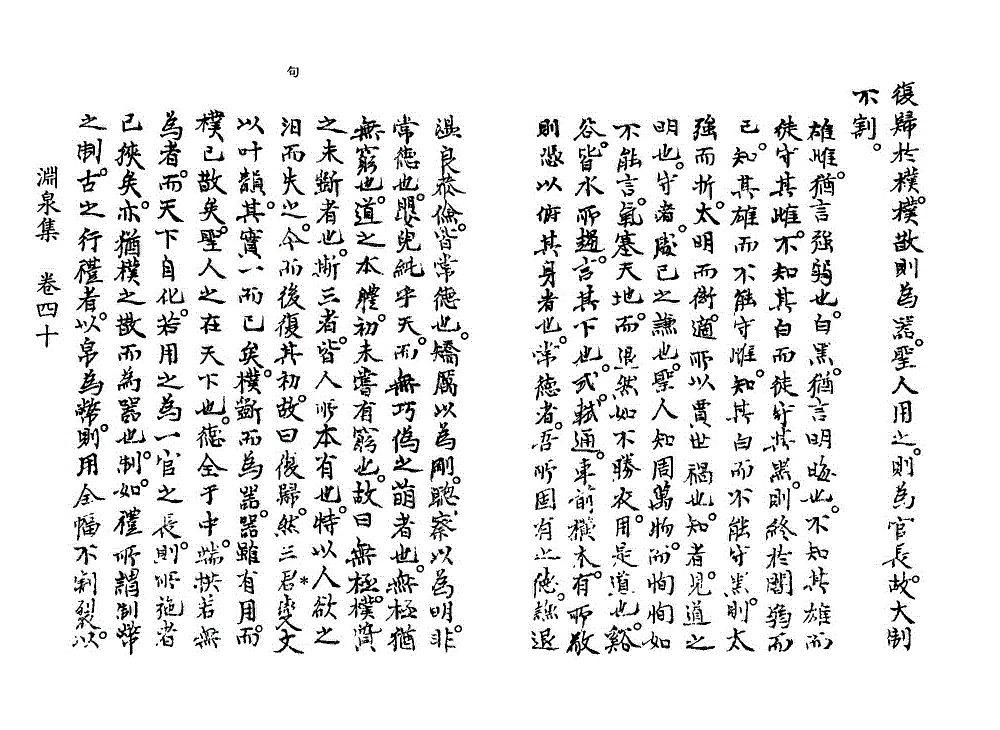 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雄雌。犹言强弱也。白黑。犹言明晦也。不知其雄而徒守其雌。不知其白而徒守其黑。则终于闇弱而已。知其雄而不能守雌。知其白而不能守黑。则太强而折。太明而衒。适所以贾世祸也。知者。见道之明也。守者。处己之谦也。圣人知周万物。而恂恂如不能言。气塞天地。而退然如不胜衣。用是道也。溪谷。皆水所趋。言其下也。式。轼通。车前横木。有所敬则凭以俯其身者也。常德者。吾所固有之德。谦退温良恭俭。皆常德也。矫厉以为刚。聪察以为明。非常德也。婴儿纯乎天。而无巧伪之萌者也。无极犹无穷也。道之本体。初未尝有穷也。故曰无极。朴质之未斲者也。斯三者。皆人所本有也。特以人欲之汩而失之。今而后复其初。故曰复归。然三句变文以叶韵。其实一而已矣。朴斲而为器。器虽有用。而朴已散矣。圣人之在天下也。德全于中。端拱若无为者。而天下自化。若用之为一官之长。则所施者已狭矣。亦犹朴之散而为器也。制。如礼所谓制币之制。古之行礼者。以帛为币。则用全幅不割裂。以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1L 页
 喻圣人之道。不可为一偏之用。此盖承上文以起下章天下不可为之意也。
喻圣人之道。不可为一偏之用。此盖承上文以起下章天下不可为之意也。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为。犹言作为也。已。语辞。天下大器也。而其去就得失。皆非人力之所能与也。若有神明以主之。故曰神器。天下之事。莫不成于自然。而败于有意。自然者。一循天则。而我无所容心者也。有意则参以己私。其欲之也必贪。其营之也必躁。其防之也必密。躁贪竞于内。而猜防密于外。虽得之必失之。虽小事。不可为也。而况于天下神器乎。呴。微嘘也。羸。弱也。载。乘也成也。隳。败也。行随。以前后言。呴吹。以微甚言。相因者也。强羸。以盛衰言。载隳。以成败言。相反者也。吴幼清曰。取天下者。德盛而人自归之。彼以智力得之者。欲成其事而反不成。故曰为者败之。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为而得。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宝器。执之在手。不须臾舍。反不能保其不陨坠也。故曰执者失之。得失存亡之相禅。如行随呴吹强羸载隳八者之相反而相因。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2H 页
 圣人知其势之必至于此也。唯不使之过盛则可以不至于衰且亡。甚也奢也泰也。皆极盛之时也。苏黄门曰。或行于前。或随于后。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强而益。或羸而损。或载而成。或隳而毁。皆物之自然。势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务得。乃欲拒而违之。其祸不覆则折。唯圣人。知其不可逆则顺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过。而天下无患矣。愚谓天下事或相因而变。或相激而反。理势自然。虽圣人。不能使之齐于一也。唯去其已甚而太过者。使不至于极而反此。盖无为之为。所以善持神器而不失也。然此章文义。终未甚畅。姑并存苏吴二说。以俟知者。
圣人知其势之必至于此也。唯不使之过盛则可以不至于衰且亡。甚也奢也泰也。皆极盛之时也。苏黄门曰。或行于前。或随于后。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强而益。或羸而损。或载而成。或隳而毁。皆物之自然。势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务得。乃欲拒而违之。其祸不覆则折。唯圣人。知其不可逆则顺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过。而天下无患矣。愚谓天下事或相因而变。或相激而反。理势自然。虽圣人。不能使之齐于一也。唯去其已甚而太过者。使不至于极而反此。盖无为之为。所以善持神器而不失也。然此章文义。终未甚畅。姑并存苏吴二说。以俟知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章欲取天下而言。夫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其势必至于用兵。用兵而败者。其祸在目前易见也。以兵得志而强天下者。人皆以为功。殊不知其祸之愈远而尤大也。苏子瞻曰。后世用兵。皆得已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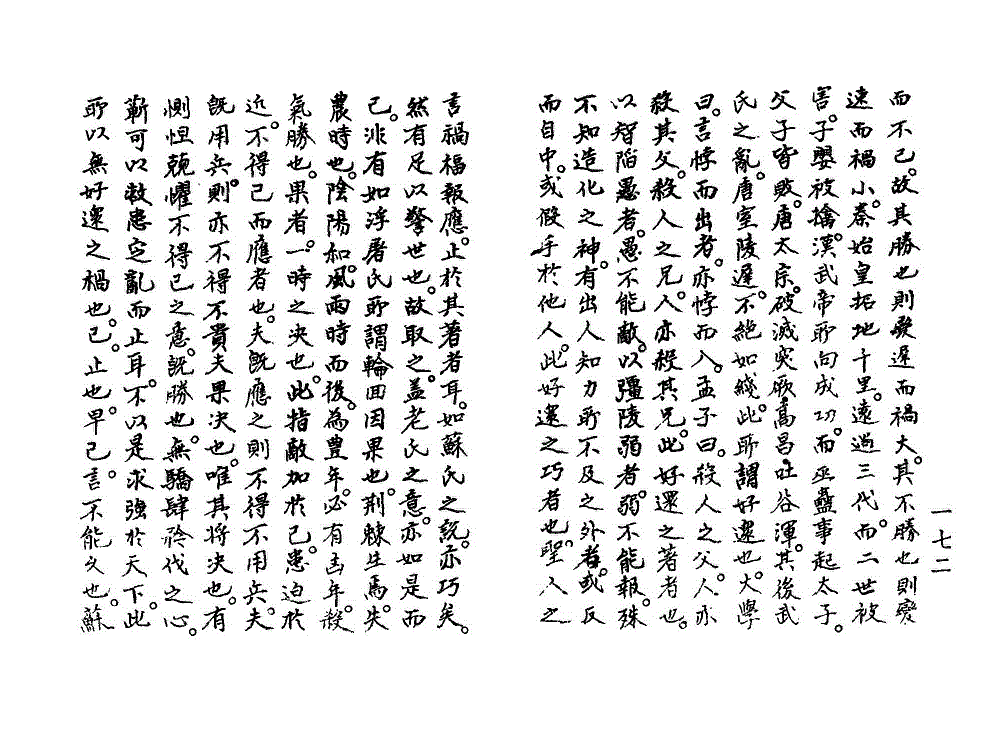 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秦始皇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二世被害。子婴被擒。汉武帝所向成功。而巫蛊事起太子。父子皆败。唐太宗。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其后武氏之乱。唐室陵迟。不绝如线。此所谓好还也。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孟子曰。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此好还之著者也。以智陷愚者。愚不能敌。以彊陵弱者。弱不能报。殊不知造化之神。有出人知力所不及之外者。或反而自中。或假手于他人。此好还之巧者也。圣人之言祸福报应。止于其著者耳。如苏氏之说。亦巧矣。然有足以警世也。故取之。盖老氏之意。亦如是而已。非有如浮屠氏所谓轮回因果也。荆棘生焉。失农时也。阴阳和。风雨时而后。为礼年。必有凶年。杀气胜也。果者。一时之决也。此指敌加于己。患迫于近。不得已而应者也。夫既应之则不得不用兵。夫既用兵。则亦不得不贵夫果决也。唯其将决也。有恻怛兢惧不得已之意。既胜也。无骄肆矜伐之心。蕲可以救患定乱而止耳。不以是求强于天下。此所以无好还之祸也。已。止也。早已。言不能久也。苏
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秦始皇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二世被害。子婴被擒。汉武帝所向成功。而巫蛊事起太子。父子皆败。唐太宗。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其后武氏之乱。唐室陵迟。不绝如线。此所谓好还也。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孟子曰。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此好还之著者也。以智陷愚者。愚不能敌。以彊陵弱者。弱不能报。殊不知造化之神。有出人知力所不及之外者。或反而自中。或假手于他人。此好还之巧者也。圣人之言祸福报应。止于其著者耳。如苏氏之说。亦巧矣。然有足以警世也。故取之。盖老氏之意。亦如是而已。非有如浮屠氏所谓轮回因果也。荆棘生焉。失农时也。阴阳和。风雨时而后。为礼年。必有凶年。杀气胜也。果者。一时之决也。此指敌加于己。患迫于近。不得已而应者也。夫既应之则不得不用兵。夫既用兵。则亦不得不贵夫果决也。唯其将决也。有恻怛兢惧不得已之意。既胜也。无骄肆矜伐之心。蕲可以救患定乱而止耳。不以是求强于天下。此所以无好还之祸也。已。止也。早已。言不能久也。苏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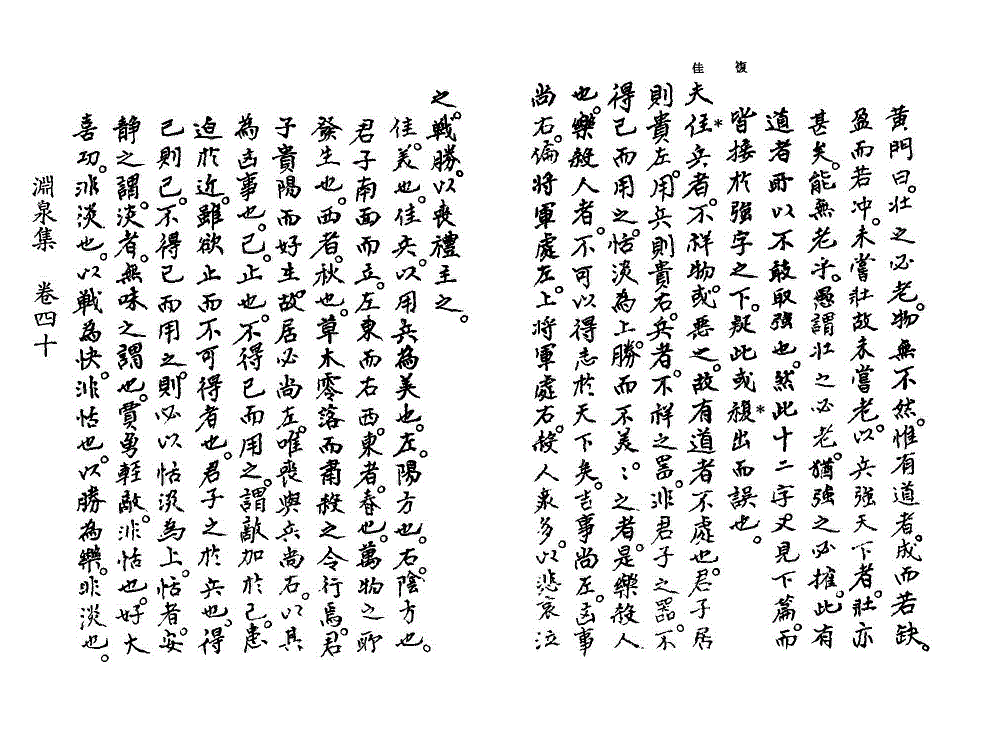 黄门曰。壮之必老。物无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尝壮故未尝老。以兵强天下者。壮亦甚矣。能无老乎。愚谓壮之必老。犹强之必摧。此有道者所以不敢取强也。然此十二字。又见下篇。而皆接于强字之下。疑此或复出而误也。
黄门曰。壮之必老。物无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尝壮故未尝老。以兵强天下者。壮亦甚矣。能无老乎。愚谓壮之必老。犹强之必摧。此有道者所以不敢取强也。然此十二字。又见下篇。而皆接于强字之下。疑此或复出而误也。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美之者。是乐杀人也。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主之。
佳。美也。佳兵。以用兵为美也。左。阳方也。右。阴方也。君子南面而立。左东而右西。东者。春也。万物之所发生也。西者。秋也。草木零落而肃杀之令行焉。君子贵阳而好生。故居必尚左。唯丧与兵尚右。以其为凶事也。已。止也。不得已而用之。谓敌加于己。患迫于近。虽欲止而不可得者也。君子之于兵也。得已则已。不得已而用之。则必以恬淡为上。恬者。安静之谓。淡者。无味之谓也。贾勇轻敌。非恬也。好大喜功。非淡也。以战为快。非恬也。以胜为乐。非淡也。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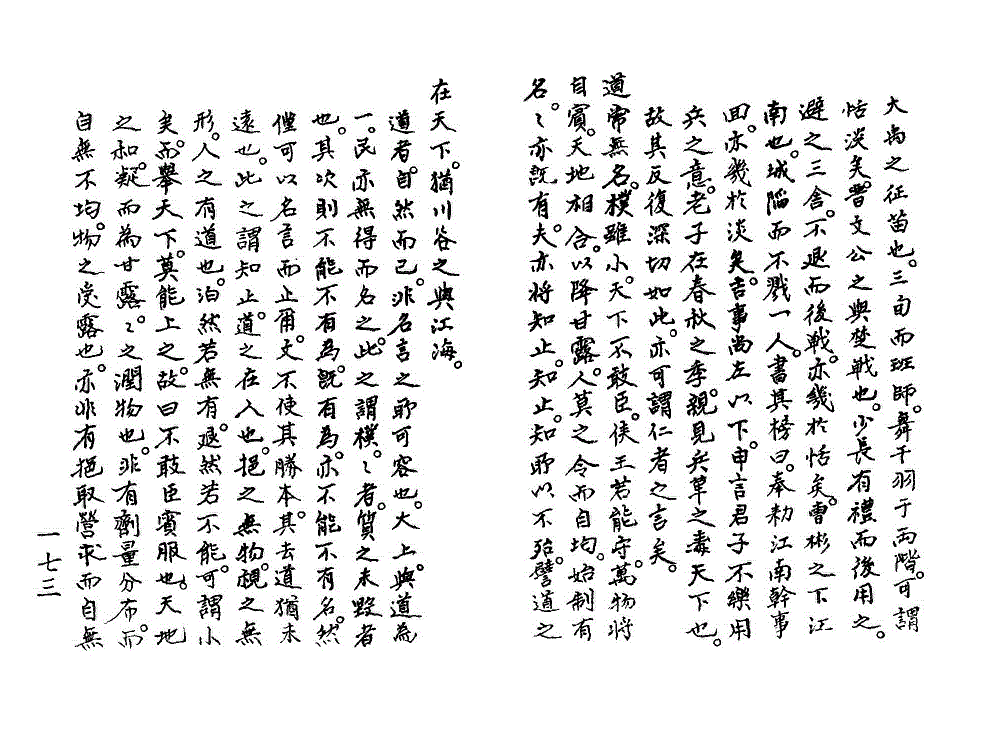 大禹之征苗也。三旬而班师。舞干羽于两阶。可谓恬淡矣。晋文公之与楚战也。少长有礼而后用之。避之三舍。不退而后战。亦几于恬矣。曹彬之下江南也。城陷而不戮一人。书其榜曰。奉敕江南干事回。亦几于淡矣。吉事尚左以下。申言君子不乐用兵之意。老子在春秋之季。亲见兵革之毒天下也。故其反复深切如此。亦可谓仁者之言矣。
大禹之征苗也。三旬而班师。舞干羽于两阶。可谓恬淡矣。晋文公之与楚战也。少长有礼而后用之。避之三舍。不退而后战。亦几于恬矣。曹彬之下江南也。城陷而不戮一人。书其榜曰。奉敕江南干事回。亦几于淡矣。吉事尚左以下。申言君子不乐用兵之意。老子在春秋之季。亲见兵革之毒天下也。故其反复深切如此。亦可谓仁者之言矣。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知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道者。自然而已。非名言之所可容也。大上。与道为一。民亦无得而名之。此之谓朴。朴者。质之未毁者也。其次则不能不有为。既有为。亦不能不有名。然仅可以名言而止尔。文不使其胜本。其去道犹未远也。此之谓知止。道之在人也。挹之无物。视之无形。人之有道也。泊然若无有。退然若不能。可谓小矣。而举天下。莫能上之。故曰不敢臣宾服也。天地之和。凝而为甘露。露之润物也。非有剂量分布。而自无不均。物之受露也。亦非有挹取营求而自无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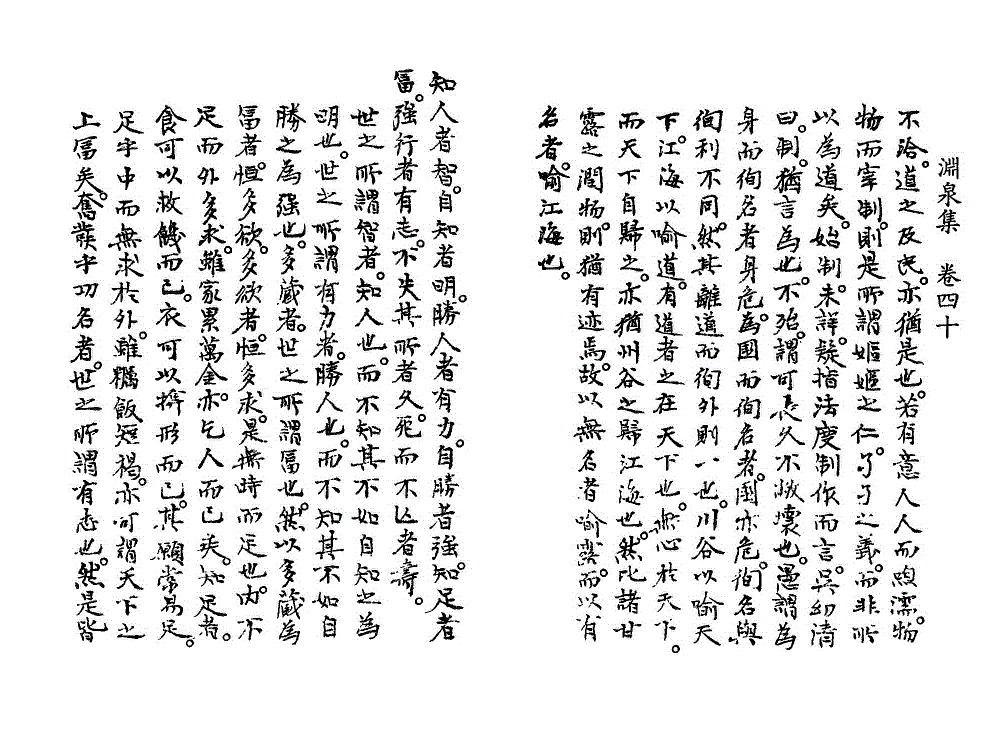 不洽。道之及民。亦犹是也。若有意人人而喣濡。物物而宰制。则是所谓妪妪之仁。孑孑之义。而非所以为道矣。始制。未详。疑指法度制作而言。吴幼清曰。制。犹言为也。不殆。谓可长久不敝坏也。愚谓为身而徇名者身危。为国而徇名者。国亦危。徇名与徇利不同。然其离道而徇外则一也。川谷以喻天下。江海以喻道。有道者之在天下也。无心于天下。而天下自归之。亦犹州谷之归江海也。然比诸甘露之润物。则犹有迹焉。故以无名者喻露。而以有名者。喻江海也。
不洽。道之及民。亦犹是也。若有意人人而喣濡。物物而宰制。则是所谓妪妪之仁。孑孑之义。而非所以为道矣。始制。未详。疑指法度制作而言。吴幼清曰。制。犹言为也。不殆。谓可长久不敝坏也。愚谓为身而徇名者身危。为国而徇名者。国亦危。徇名与徇利不同。然其离道而徇外则一也。川谷以喻天下。江海以喻道。有道者之在天下也。无心于天下。而天下自归之。亦犹州谷之归江海也。然比诸甘露之润物。则犹有迹焉。故以无名者喻露。而以有名者。喻江海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世之所谓智者。知人也。而不知其不如自知之为明也。世之所谓有力者。胜人也。而不知其不如自胜之为强也。多藏者。世之所谓富也。然以多藏为富者。恒多欲。多欲者。恒多求。是无时而足也。内不足而外多求。虽家累万金。亦乞人而已矣。知足者。食可以救饥而已。衣可以掩形而已。其愿常易足。足乎中而无求于外。虽粝饭短褐。亦可谓天下之上富矣。奋发乎功名者。世之所谓有志也。然是皆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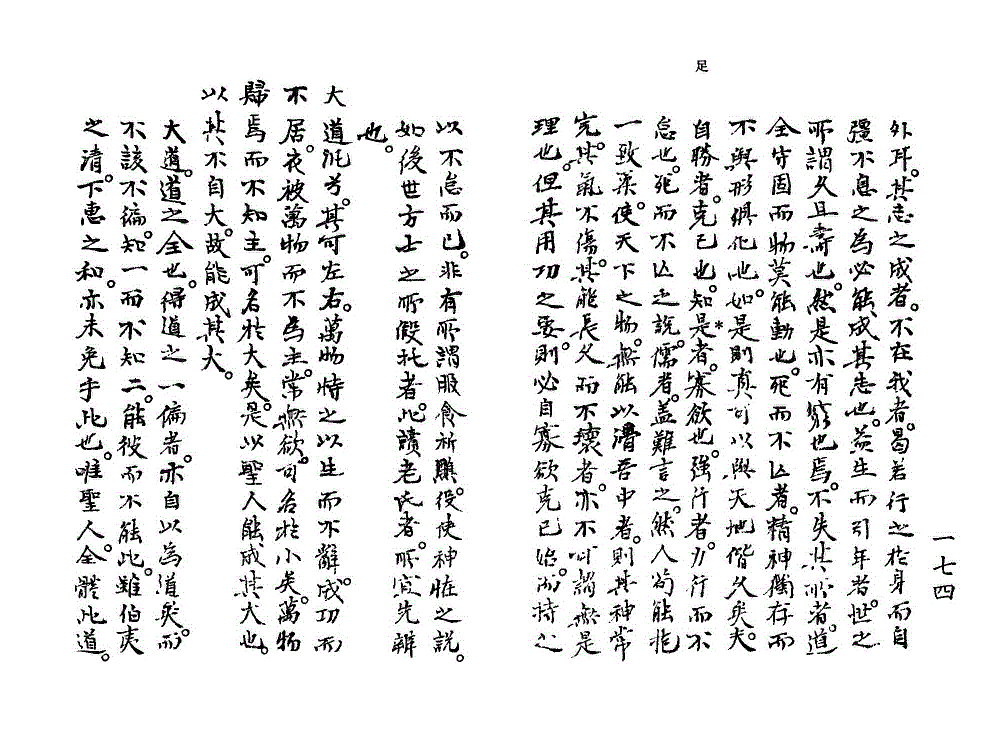 外耳。其志之成者。不在我者。曷若行之于身而自彊不息之为必能成其志也。益生而引年者。世之所谓久且寿也。然是亦有穷也焉。不失其所者。道全守固而物莫能动也。死而不亡者。精神独存而不与形俱化也。如是则真可以与天地偕久矣。夫自胜者。克己也。知足者。寡欲也。强行者。力行而不怠也。死而不亡之说。儒者。盖难言之。然人苟能抱一致柔。使天下之物。无能以滑吾中者。则其神常完。其气不伤。其能长久而不坏者。亦不可谓无是理也。但其用功之要。则必自寡欲克己始。而持之以不怠而已。非有所谓服食祈醮。役使神怪之说。如后世方士之所假托者。此读老氏者。所宜先辨也。
外耳。其志之成者。不在我者。曷若行之于身而自彊不息之为必能成其志也。益生而引年者。世之所谓久且寿也。然是亦有穷也焉。不失其所者。道全守固而物莫能动也。死而不亡者。精神独存而不与形俱化也。如是则真可以与天地偕久矣。夫自胜者。克己也。知足者。寡欲也。强行者。力行而不怠也。死而不亡之说。儒者。盖难言之。然人苟能抱一致柔。使天下之物。无能以滑吾中者。则其神常完。其气不伤。其能长久而不坏者。亦不可谓无是理也。但其用功之要。则必自寡欲克己始。而持之以不怠而已。非有所谓服食祈醮。役使神怪之说。如后世方士之所假托者。此读老氏者。所宜先辨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成功而不居。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矣。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道之全也。得道之一偏者。亦自以为道矣。而不该不遍。知一而不知二。能彼而不能此。虽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亦未免乎此也。唯圣人。全体此道。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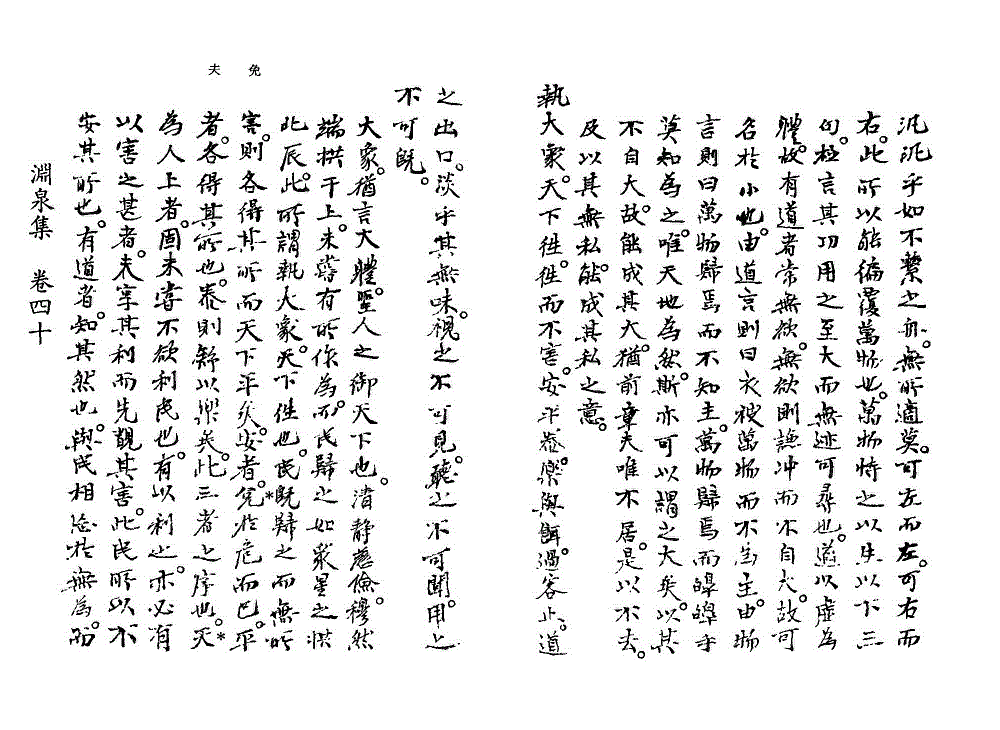 汎汎乎如不系之舟。无所适莫。可左而左。可右而右。此所以能遍覆万物也。万物恃之以生以下三句。极言其功用之至大而无迹可寻也。道以虚为体。故有道者常无欲。无欲则谦冲而不自大。故可名于小也。由道言则曰衣被万物而不为主。由物言则曰万物归焉而不知主。万物归焉而皞皞乎莫知为之。唯天地为然。斯亦可以谓之大矣。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犹前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及以其无私。能成其私之意。
汎汎乎如不系之舟。无所适莫。可左而左。可右而右。此所以能遍覆万物也。万物恃之以生以下三句。极言其功用之至大而无迹可寻也。道以虚为体。故有道者常无欲。无欲则谦冲而不自大。故可名于小也。由道言则曰衣被万物而不为主。由物言则曰万物归焉而不知主。万物归焉而皞皞乎莫知为之。唯天地为然。斯亦可以谓之大矣。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犹前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及以其无私。能成其私之意。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
大象。犹言大体。圣人之御天下也。清静慈俭。穆然端拱于上。未尝有所作为。而民归之如众星之拱北辰。此所谓执大象。天下往也。民既归之而无所害。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安者。免于危而已。平者。各得其所也。泰则舒以乐矣。此三者之序也。夫为人上者。固未尝不欲利民也。有以利之。亦必有以害之甚者。未享其利而先睹其害。此民所以不安其所也。有道者。知其然也。与民相忘于无为。而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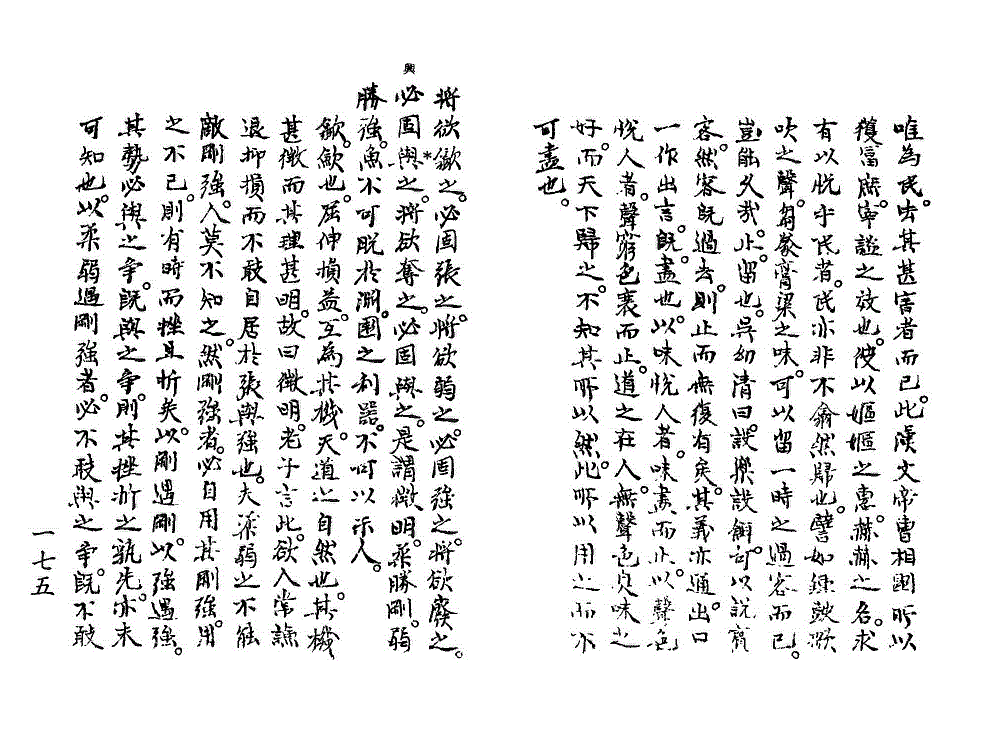 唯为民。去其甚害者而已。此汉文帝曹相国所以获富庶。宁谧之效也。彼以妪妪之惠。赫赫之名。求有以悦乎民者。民亦非不翕然归也。譬如钟鼓歌吹之声。刍豢膏粱之味。可以留一时之过客而已。岂能久哉。止。留也。吴幼清曰。设乐设饵。可以说宾客。然客既过去。则止而无复有矣。其义亦通。出口一作出言。既。尽也。以味悦人者。味尽而止。以声色悦人者。声穷色衰而止。道之在人。无声色臭味之好。而天下归之。不知其所以然。此所以用之而不可尽也。
唯为民。去其甚害者而已。此汉文帝曹相国所以获富庶。宁谧之效也。彼以妪妪之惠。赫赫之名。求有以悦乎民者。民亦非不翕然归也。譬如钟鼓歌吹之声。刍豢膏粱之味。可以留一时之过客而已。岂能久哉。止。留也。吴幼清曰。设乐设饵。可以说宾客。然客既过去。则止而无复有矣。其义亦通。出口一作出言。既。尽也。以味悦人者。味尽而止。以声色悦人者。声穷色衰而止。道之在人。无声色臭味之好。而天下归之。不知其所以然。此所以用之而不可尽也。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歙。敛也。屈伸损益。互为其机。天道之自然也。其机甚微而其理甚明。故曰微明。老子言此。欲人常谦退抑损而不敢自居于张与强也。夫柔弱之不能敌刚强。人莫不知之。然刚强者。必自用其刚强。用之不已。则有时而挫且折矣。以刚遇刚。以强遇强。其势必与之争。既与之争。则其挫折之孰先。亦未可知也。以柔弱遇刚强者。必不敢与之争。既不敢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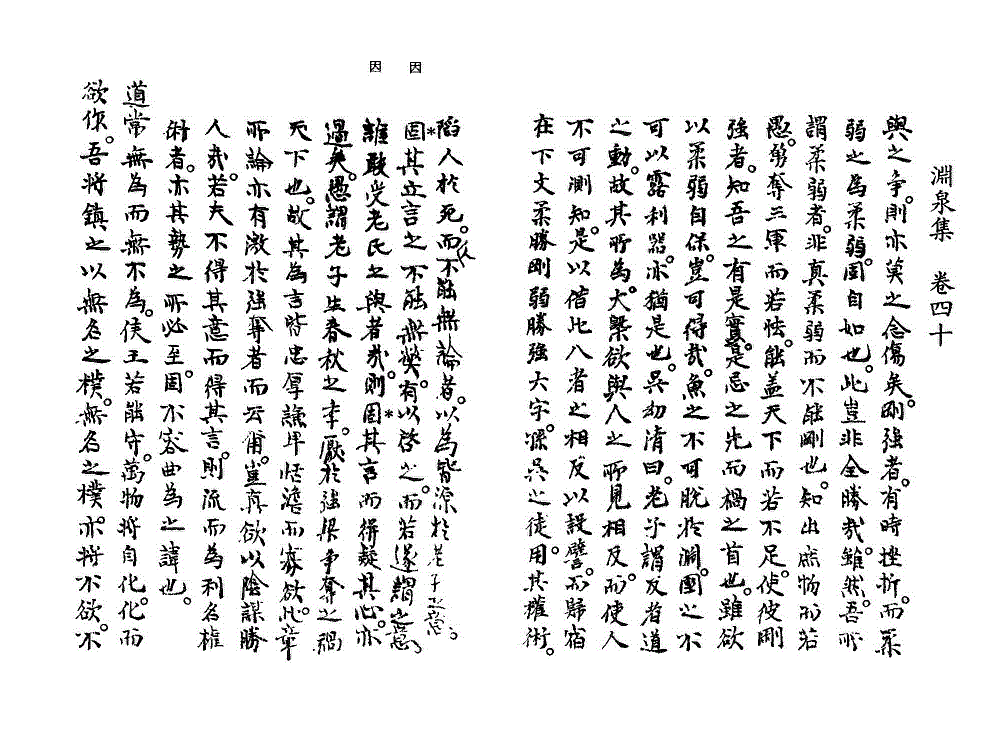 与之争。则亦莫之念伤矣。刚强者。有时挫折。而柔弱之为柔弱。固自如也。此岂非全胜哉。虽然。吾所谓柔弱者。非真柔弱而不能刚也。知出庶物而若愚。勇夺三军而若怯。能盖天下而若不足。使彼刚强者。知吾之有是实。是忌之先而祸之首也。虽欲以柔弱自保。岂可得哉。鱼之不可脱于渊。国之不可以露利器。亦犹是也。吴幼清曰。老子谓反者道之动。故其所为。大槩欲与人之所见相反。而使人不可测知。是以借此八者之相反以设譬。而归宿在下文柔胜刚弱胜强六字。孙吴之徒。用其权术。陷人于死。而人不能无论者。以为皆源于老子之意。因其立言之不能无弊。有以启之。而若遂谓之意。谁敢受老氏之与者哉。则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过矣。愚谓老子生春秋之季。厌于强梁争夺之祸天下也。故其为言皆忠厚谦卑恬澹而寡欲。此章所论亦有激于强夺者而云尔。岂真欲以阴谋胜人哉。若夫不得其意而得其言。则流而为利名权术者。亦其势之所必至。固不容曲为之讳也。
与之争。则亦莫之念伤矣。刚强者。有时挫折。而柔弱之为柔弱。固自如也。此岂非全胜哉。虽然。吾所谓柔弱者。非真柔弱而不能刚也。知出庶物而若愚。勇夺三军而若怯。能盖天下而若不足。使彼刚强者。知吾之有是实。是忌之先而祸之首也。虽欲以柔弱自保。岂可得哉。鱼之不可脱于渊。国之不可以露利器。亦犹是也。吴幼清曰。老子谓反者道之动。故其所为。大槩欲与人之所见相反。而使人不可测知。是以借此八者之相反以设譬。而归宿在下文柔胜刚弱胜强六字。孙吴之徒。用其权术。陷人于死。而人不能无论者。以为皆源于老子之意。因其立言之不能无弊。有以启之。而若遂谓之意。谁敢受老氏之与者哉。则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过矣。愚谓老子生春秋之季。厌于强梁争夺之祸天下也。故其为言皆忠厚谦卑恬澹而寡欲。此章所论亦有激于强夺者而云尔。岂真欲以阴谋胜人哉。若夫不得其意而得其言。则流而为利名权术者。亦其势之所必至。固不容曲为之讳也。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
渊泉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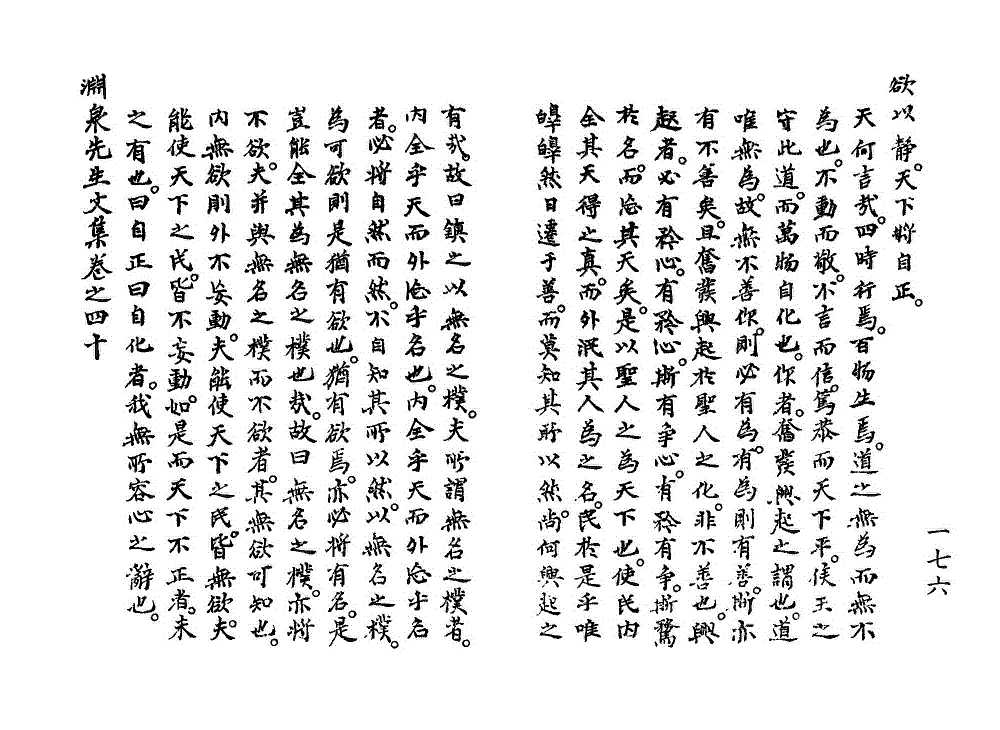 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之无为而无不为也。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笃恭而天下平。侯王之守此道。而万物自化也。作者。奋发兴起之谓也。道唯无为。故无不善作。则必有为。有为则有善。斯亦有不善矣。且奋发兴起于圣人之化。非不善也。兴起者。必有矜心。有矜心。斯有争心。有矜有争。斯骛于名。而忘其天矣。是以圣人之为天下也。使民内全其天得之真。而外泯其人为之名。民于是乎唯皞皞然日迁于善。而莫知其所以然。尚何兴起之有哉。故曰镇之以无名之朴。夫所谓无名之朴者。内全乎天而外忘乎名也。内全乎天而外忘乎名者。必将自然而然。不自知其所以然。以无名之朴。为可欲则是犹有欲也。犹有欲焉。亦必将有名。是岂能全其为无名之朴也哉。故曰无名之朴。亦将不欲。夫并与无名之朴而不欲者。其无欲可知也。内无欲则外不妄动。夫能使天下之民。皆无欲。夫能使天下之民。皆不妄动。如是而天下不正者。未之有也。曰自正曰自化者。我无所容心之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