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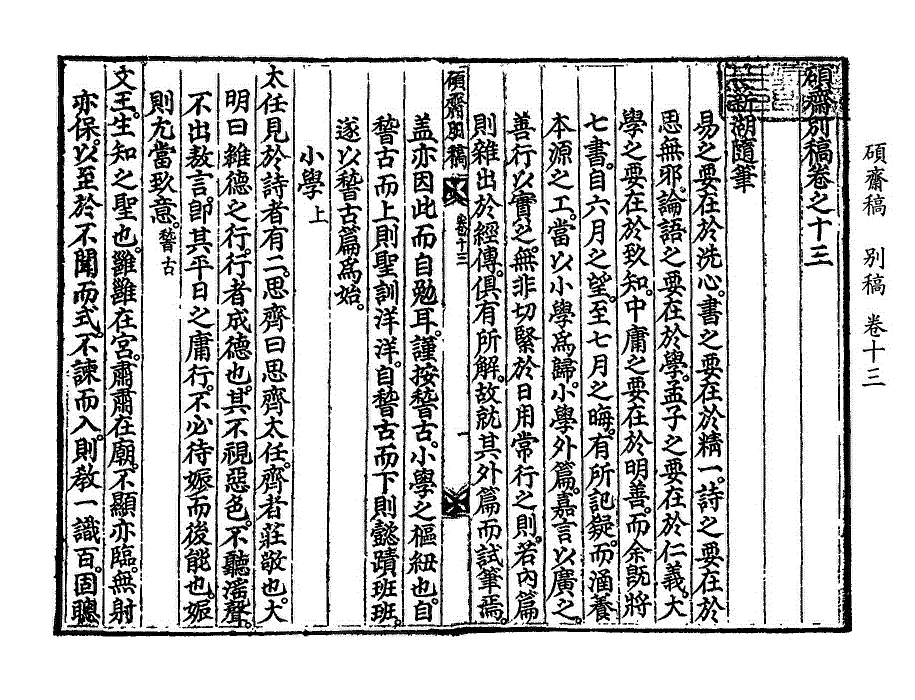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易之要在于洗心。书之要在于精一。诗之要在于思无邪。论语之要在于学。孟子之要在于仁义。大学之要在于致知。中庸之要在于明善。而余既将七书。自六月之望。至七月之晦。有所记疑。而涵养本源之工。当以小学为归。小学外篇。嘉言以广之。善行以实之。无非切紧于日用常行之则。若内篇则杂出于经传。俱有所解。故就其外篇而试笔焉。盖亦因此而自勉耳。谨按稽古。小学之枢纽也。自稽古而上则圣训洋洋。自稽古而下则懿迹班班。遂以稽古篇为始。
小学[上]
太任见于诗者有二。思齐曰思齐太任。齐者庄敬也。大明曰维德之行。行者成德也。其不视恶色。不听淫声。不出敖言。即其平日之庸行。不必待娠而后能也。娠则尤当致意。(稽古)
文王。生知之圣也。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以至于不闻而式。不谏而入。则教一识百。固聪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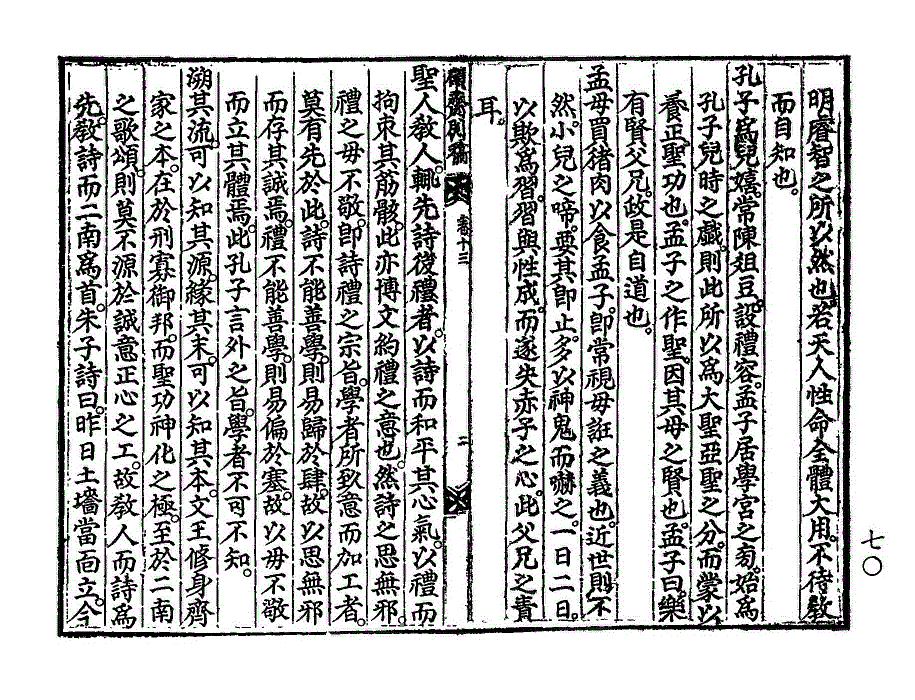 明睿智之所以然也。若天人性命全体大用。不待教而自知也。
明睿智之所以然也。若天人性命全体大用。不待教而自知也。孔子为儿嬉。常陈俎豆。设礼容。孟子居学宫之旁。始为孔子儿时之戏。则此所以为大圣亚圣之分。而蒙以养正圣功也。孟子之作圣。因其母之贤也。孟子曰。乐有贤父兄。政是自道也。
孟母买猪肉以食孟子。即常视毋诳之义也。近世则不然。小儿之啼。要其即止。多以神鬼而吓之。一日二日。以欺为习。习与性成。而遂失赤子之心。此父兄之责耳。
圣人教人。辄先诗后礼者。以诗而和平其心气。以礼而拘束其筋骸。此亦博文约礼之意也。然诗之思无邪。礼之毋不敬。即诗礼之宗旨。学者所致意而加工者。莫有先于此。诗不能善学。则易归于肆。故以思无邪而存其诚焉。礼不能善学。则易偏于塞。故以毋不敬而立其体焉。此孔子言外之旨。学者不可不知。
溯其流。可以知其源。缘其末。可以知其本。文王修身齐家之本。在于刑寡御邦。而圣功神化之极。至于二南之歌颂。则莫不源于诚意正心之工。故教人而诗为先。教诗而二南为首。朱子诗曰。昨日土墙当面立。今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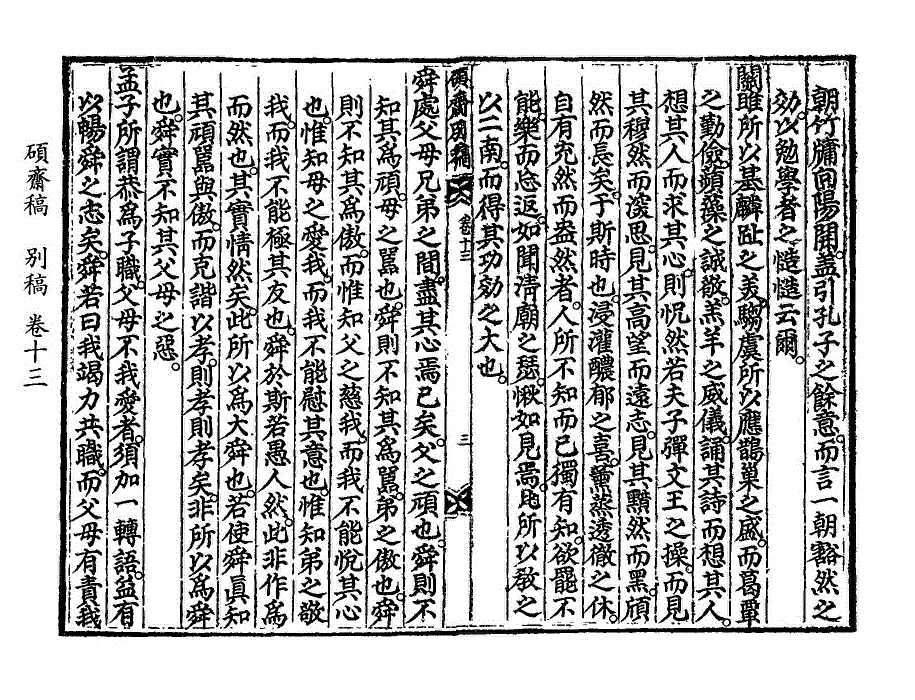 朝竹牖向阳开。盖引孔子之馀意。而言一朝豁然之效。以勉学者之慥慥云尔。
朝竹牖向阳开。盖引孔子之馀意。而言一朝豁然之效。以勉学者之慥慥云尔。关雎所以基麟趾之美。驺虞所以应鹊巢之盛。而葛覃之勤俭。蘋藻之诚敬。羔羊之威仪。诵其诗而想其人。想其人而求其心。则恍然若夫子弹文王之操。而见其穆然而深思。见其高望而远志。见其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矣。于斯时也。浸灌醲郁之喜。薰蒸透彻之休。自有充然而盎然者。人所不知而己独有知。欲罢不能。乐而忘返。如闻清庙之瑟。愀如见焉。此所以教之以二南。而得其功效之大也。
舜处父母兄弟之间。尽其心焉已矣。父之顽也。舜则不知其为顽。母之嚚也。舜则不知其为嚚。弟之傲也。舜则不知其为傲。而惟知父之慈我。而我不能悦其心也。惟知母之爱我。而我不能慰其意也。惟知弟之敬我。而我不能极其友也。舜于斯若愚人然。此非作为而然也。其实情然矣。此所以为大舜也。若使舜真知其顽嚚与傲。而克谐以孝。则孝则孝矣。非所以为舜也。舜实不知其父母之恶。
孟子所谓恭为子职。父母不我爱者。须加一转语。益有以畅舜之志矣。舜若曰我竭力共职。而父母有责我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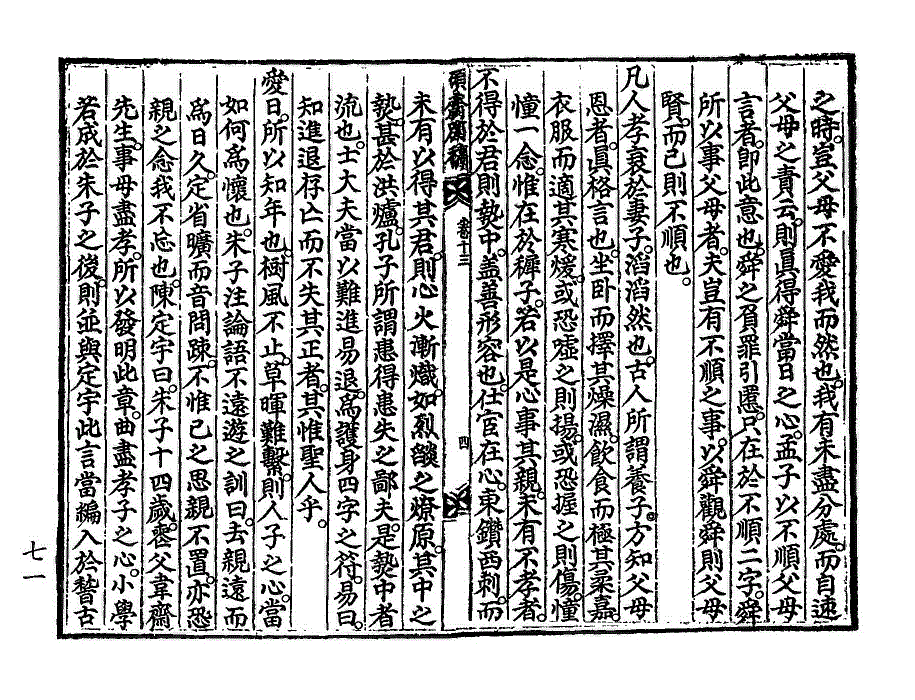 之时。岂父母不爱我而然也。我有未尽分处。而自速父母之责云。则真得舜当日之心。孟子以不顺父母言者。即此意也。舜之负罪引慝。只在于不顺二字。舜所以事父母者。夫岂有不顺之事。以舜观舜则父母贤。而己则不顺也。
之时。岂父母不爱我而然也。我有未尽分处。而自速父母之责云。则真得舜当日之心。孟子以不顺父母言者。即此意也。舜之负罪引慝。只在于不顺二字。舜所以事父母者。夫岂有不顺之事。以舜观舜则父母贤。而己则不顺也。凡人孝衰于妻子。滔滔然也。古人所谓养子。方知父母恩者。真格言也。坐卧而择其燥湿。饮食而极其柔嘉。衣服而适其寒煖。或恐嘘之则扬。或恐握之则伤。憧憧一念。惟在于稚子。若以是心事其亲。未有不孝者。
不得于君则热中。盖善形容也。仕宦在心。东钻西刺。而未有以得其君。则心火渐炽。如烈燄之燎原。其中之热。甚于洪炉。孔子所谓患得患失之鄙夫。是热中者流也。士大夫当以难进易退。为护身四字之符。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爱日。所以知年也。树风不止。草晖难系。则人子之心。当如何为怀也。朱子注论语不远游之训曰。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陈定宇曰。朱子十四岁。丧父韦斋先生。事母尽孝。所以发明此章。曲尽孝子之心。小学若成于朱子之后。则并与定宇此言当编入于稽古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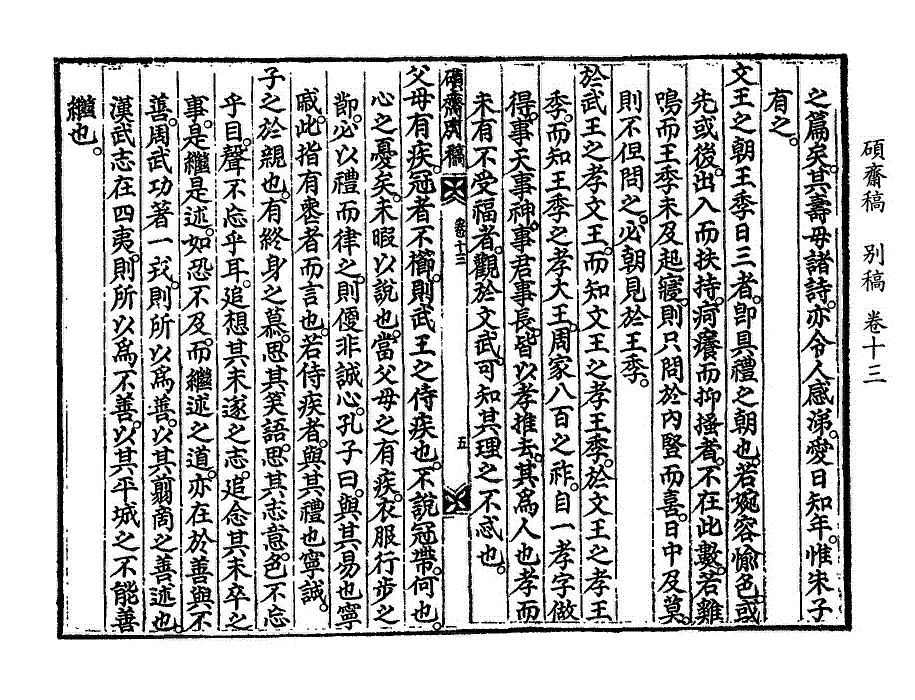 之篇矣。其寿母诸诗。亦令人感涕。爱日知年。惟朱子有之。
之篇矣。其寿母诸诗。亦令人感涕。爱日知年。惟朱子有之。文王之朝王季日三者。即具礼之朝也。若婉容愉色。或先或后。出入而扶持。疴痒而抑搔者。不在此数。若鸡鸣而王季未及起寝。则只问于内竖而喜。日中及莫。则不但问之。必朝见于王季。
于武王之孝文王。而知文王之孝王季。于文王之孝王季。而知王季之孝大王。周家八百之祚。自一孝字做得。事天事神。事君事长。皆以孝推去。其为人也孝而未有不受福者。观于文武。可知其理之不忒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则武王之侍疾也。不说冠带。何也。心之忧矣。未暇以说也。当父母之有疾。衣服行步之节。必以礼而律之。则便非诚心。孔子曰。与其易也宁戚。此指有丧者而言也。若侍疾者。与其礼也宁诚。
子之于亲也。有终身之慕。思其笑语。思其志意。色不忘乎目。声不忘乎耳。追想其未遂之志。追念其未卒之事。是继是述。如恐不及。而继述之道。亦在于善与不善。周武功著一戎。则所以为善。以其剪商之善述也。汉武志在四夷。则所以为不善。以其平城之不能善继也。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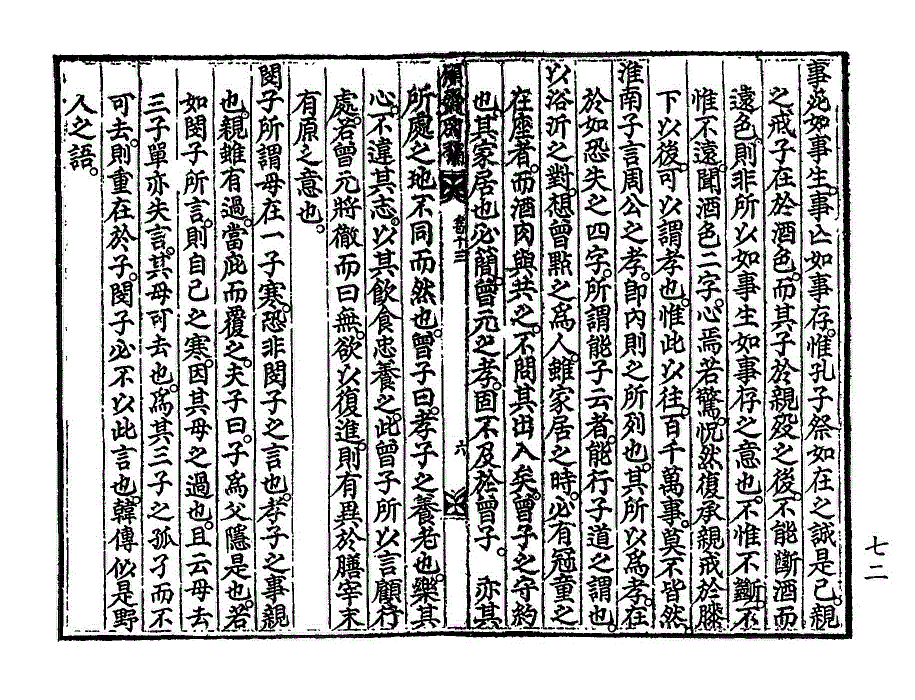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惟孔子祭如在之诚是已。亲之戒子在于酒色。而其子于亲殁之后。不能断酒而远色。则非所以如事生如事存之意也。不惟不断。不惟不远。闻酒色二字。心焉若惊。恍然复承亲戒于膝下以后。可以谓孝也。惟此以往。百千万事。莫不皆然。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惟孔子祭如在之诚是已。亲之戒子在于酒色。而其子于亲殁之后。不能断酒而远色。则非所以如事生如事存之意也。不惟不断。不惟不远。闻酒色二字。心焉若惊。恍然复承亲戒于膝下以后。可以谓孝也。惟此以往。百千万事。莫不皆然。淮南子言周公之孝。即内则之所列也。其所以为孝。在于如恐失之四字。所谓能子云者。能行子道之谓也。
以浴沂之对。想曾点之为人。虽家居之时。必有冠童之在座者。而酒肉与共之。不问其出入矣。曾子之守约也。其家居也必简。曾元之孝。固不及于曾子。 亦其所处之地不同而然也。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忠养之。此曾子所以言顾行处。若曾元将彻而曰无。欲以复进。则有异于膳宰末有原之意也。
闵子所谓母在一子寒。恐非闵子之言也。孝子之事亲也。亲虽有过。当庇而覆之。夫子曰。子为父隐是也。若如闵子所言。则自己之寒。因其母之过也。且云母去三子单亦失言。其母可去也。为其三子之孤孑而不可去。则重在于子。闵子必不以此言也。韩传似是野人之语。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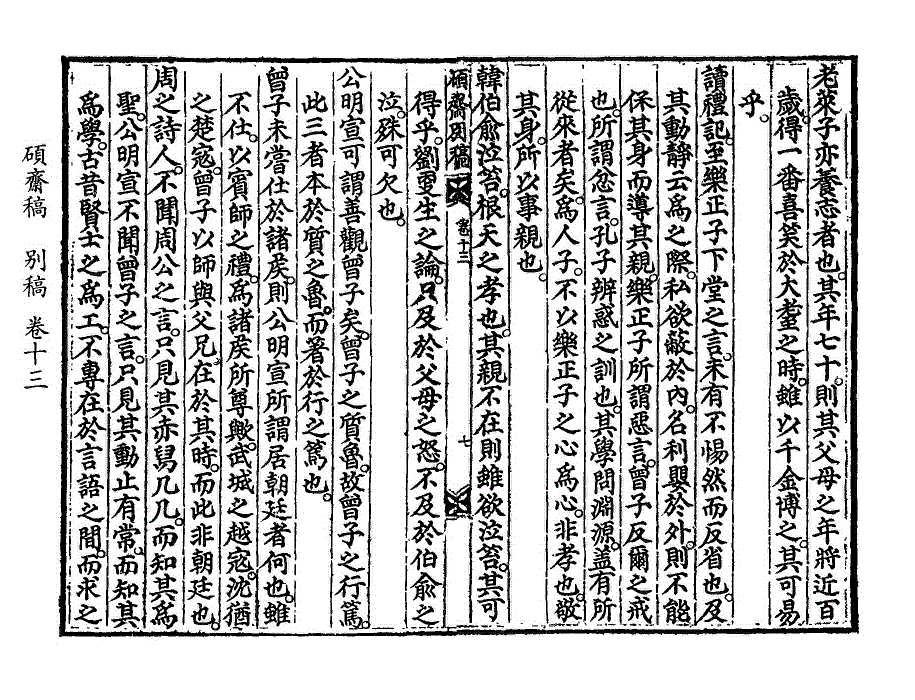 老莱子亦养志者也。其年七十。则其父母之年将近百岁。得一番喜笑于大耋之时。虽以千金博之。其可易乎。
老莱子亦养志者也。其年七十。则其父母之年将近百岁。得一番喜笑于大耋之时。虽以千金博之。其可易乎。读礼记。至乐正子下堂之言。未有不惕然而反省也。及其动静云为之际。私欲蔽于内。名利婴于外。则不能保其身而导其亲。乐正子所谓恶言。曾子反尔之戒也。所谓忿言。孔子辨惑之训也。其学问渊源。盖有所从来者矣。为人子。不以乐正子之心为心。非孝也。敬其身。所以事亲也。
韩伯俞泣笞。根天之孝也。其亲不在则虽欲泣笞。其可得乎。刘更生之论。只及于父母之怒。不及于伯俞之泣。殊可欠也。
公明宣可谓善观曾子矣。曾子之质鲁。故曾子之行笃。此三者本于质之鲁。而著于行之笃也。
曾子未尝仕于诸侯。则公明宣所谓居朝廷者何也。虽不仕。以宾师之礼。为诸侯所尊欤。武城之越寇。沈犹之楚寇。曾子以师与父兄。在于其时。而此非朝廷也。
周之诗人。不闻周公之言。只见其赤舄几几。而知其为圣。公明宣不闻曾子之言。只见其动止有常。而知其为学。古昔贤士之为工。不专在于言语之间。而求之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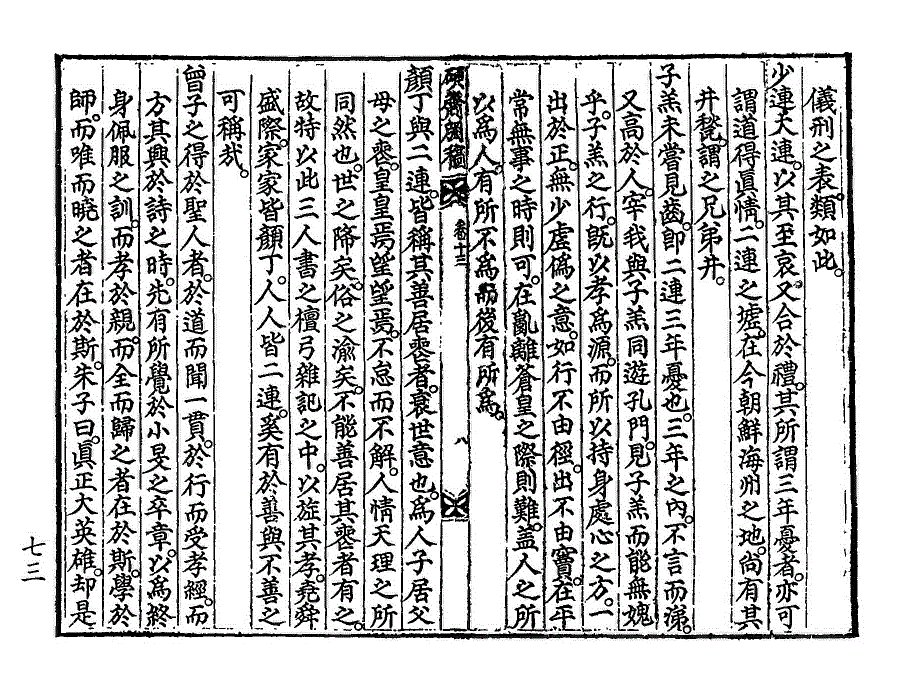 仪刑之表。类如此。
仪刑之表。类如此。少连,大连。以其至哀。又合于礼。其所谓三年忧者。亦可谓道得真情。二连之墟。在今朝鲜海州之地。尚有其井甃。谓之兄弟井。
子羔未尝见齿。即二连三年忧也。三年之内。不言而涕。又高于人。宰我与子羔同游孔门。见子羔而能无愧乎。子羔之行。既以孝为源。而所以持身处心之方。一出于正。无少虚伪之意。如行不由径。出不由窦。在平常无事之时则可。在乱离苍皇之际则难。盖人之所以为人。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颜丁与二连。皆称其善居丧者。衰世意也。为人子居父母之丧。皇皇焉望望焉。不怠而不解。人情天理之所同然也。世之降矣。俗之渝矣。不能善居其丧者有之。故特以此三人书之檀弓杂记之中。以㫌其孝。尧舜盛际。家家皆颜丁。人人皆二连。奚有于善与不善之可称哉。
曾子之得于圣人者。于道而闻一贯。于行而受孝经。而方其兴于诗之时。先有所觉于小旻之卒章。以为终身佩服之训。而孝于亲。而全而归之者在于斯。学于师。而唯而晓之者在于斯。朱子曰。真正大英雄。却是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4H 页
 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于乎曾子有之。
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于乎曾子有之。纣为象箸。箕子谏之。不听。象者象之齿也。禹贡齿革所以成车甲。自夏禹之时。以象齿为车饰。则纣以为箸。恐不至于太侈。然则箕子何为而谏也。盖禹贡齿革之为车甲。后儒之曲解也。孔子曰。乘殷之辂。取其木也。殷因夏礼。则夏辂之亦以木而不以象齿。可以类推也。及周礼作而五辂始焉。象辂居其一。因周辂之象饰。意夏辂之如周。而以禹贡之齿谓之成车者误也。大抵商纣之前。无以象齿为器者。至纣而为著。则创有之物也。故箕子以为象可以为著。玉之为杯。次第事耳。乃极言以谏之。然则公刘之时比商纣。亦可谓古矣。窜在西戎。犹以玉瑶而舟之。则以万乘之君。不可以为象箸欤。公刘之所舟者。后世之所追述也。极言其威仪之美。故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不以辞而害意可也。若如是而解诗。则文王伐崇之临冲。真为上天之所与欤。武王圣人也。西旅贡獒。召公尚戒之。况以纣之暴虐。以象为箸。其渐不可长也。其微不可已也。故防其微而杜其渐也。史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纣赦西伯。赐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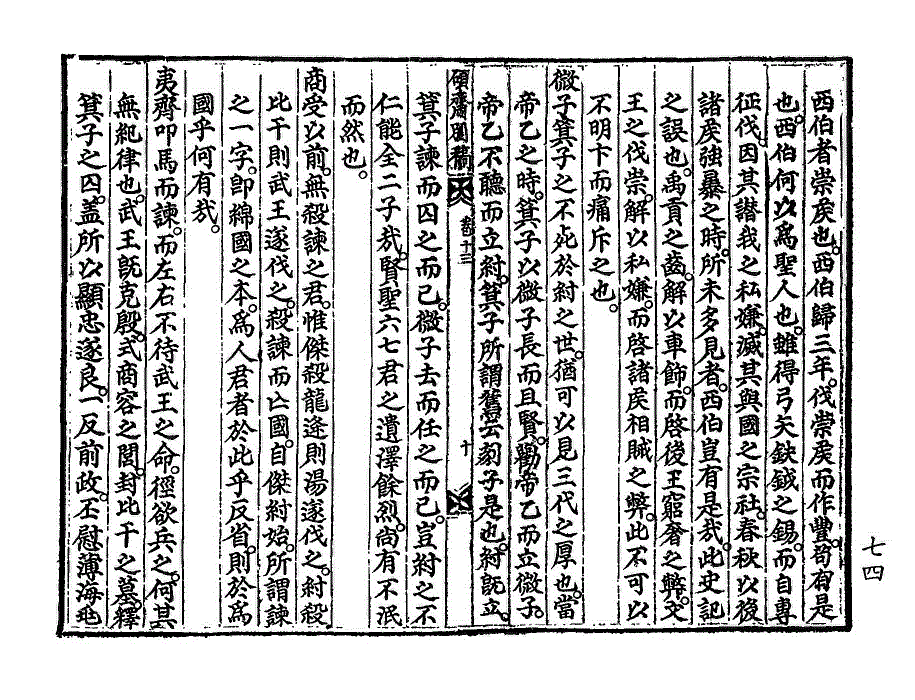 西伯者崇侯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而作丰。苟有是也。西伯何以为圣人也。虽得弓矢鈇钺之锡。而自专征伐。因其谮我之私嫌。灭其与国之宗社。春秋以后诸侯强㬥之时。所未多见者。西伯岂有是哉。此史记之误也。禹贡之齿。解以车饰。而启后王穷奢之弊。文王之伐崇。解以私嫌。而启诸侯相贼之弊。此不可以不明卞而痛斥之也。
西伯者崇侯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而作丰。苟有是也。西伯何以为圣人也。虽得弓矢鈇钺之锡。而自专征伐。因其谮我之私嫌。灭其与国之宗社。春秋以后诸侯强㬥之时。所未多见者。西伯岂有是哉。此史记之误也。禹贡之齿。解以车饰。而启后王穷奢之弊。文王之伐崇。解以私嫌。而启诸侯相贼之弊。此不可以不明卞而痛斥之也。微子,箕子之不死于纣之世。犹可以见三代之厚也。当帝乙之时。箕子以微子长而且贤。劝帝乙而立微子。帝乙不听而立纣。箕子所谓旧云刻子是也。纣既立。箕子谏而囚之而已。微子去而任之而已。岂纣之不仁能全二子哉。贤圣六七君之遗泽馀烈。尚有不泯而然也。
商受以前。无杀谏之君。惟杰杀龙逄则汤遂伐之。纣杀比干则武王遂伐之。杀谏而亡国。自杰纣始。所谓谏之一字。即绵国之本。为人君者于此乎反省。则于为国乎何有哉。
夷齐叩马而谏。而左右不待武王之命。径欲兵之。何其无纪律也。武王既克殷。式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盖所以显忠遂良。一反前政。丕慰薄海兆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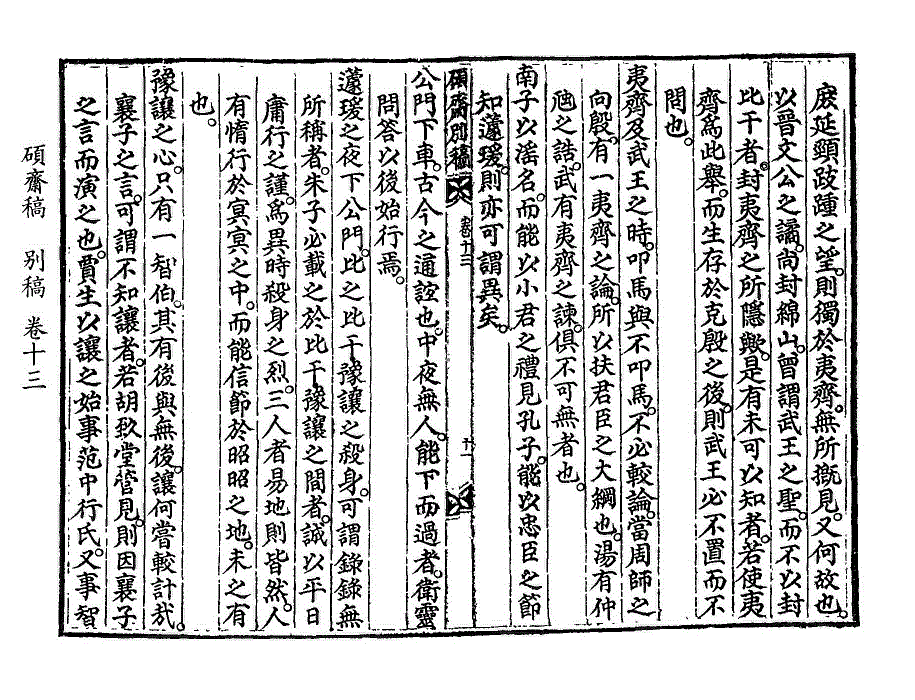 庶延颈跂踵之望。则独于夷齐。无所概见。又何故也。以晋文公之谲。尚封绵山。曾谓武王之圣。而不以封比干者。封夷齐之所隐欤。是有未可以知者。若使夷齐为此举。而生存于克殷之后。则武王必不置而不问也。
庶延颈跂踵之望。则独于夷齐。无所概见。又何故也。以晋文公之谲。尚封绵山。曾谓武王之圣。而不以封比干者。封夷齐之所隐欤。是有未可以知者。若使夷齐为此举。而生存于克殷之后。则武王必不置而不问也。夷齐及武王之时。叩马与不叩马。不必较论。当周师之向殷。有一夷齐之论。所以扶君臣之大纲也。汤有仲虺之诰。武有夷齐之谏。俱不可无者也。
南子以淫名。而能以小君之礼见孔子。能以忠臣之节知蘧瑗。则亦可谓异矣。
公门下车。古今之通谊也。中夜无人。能下而过者。卫灵问答以后始行焉。
蘧瑗之夜下公门。比之比干,豫让之杀身。可谓录录无所称者。朱子必载之于比干,豫让之间者。诚以平日庸行之谨。为异时杀身之烈。三人者易地则皆然。人有惰行于冥冥之中。而能信节于昭昭之地。未之有也。
豫让之心。只有一智伯。其有后与无后。让何尝较计哉。襄子之言。可谓不知让者。若胡致堂管见。则因襄子之言而演之也。贾生以让之始事范中行氏。又事智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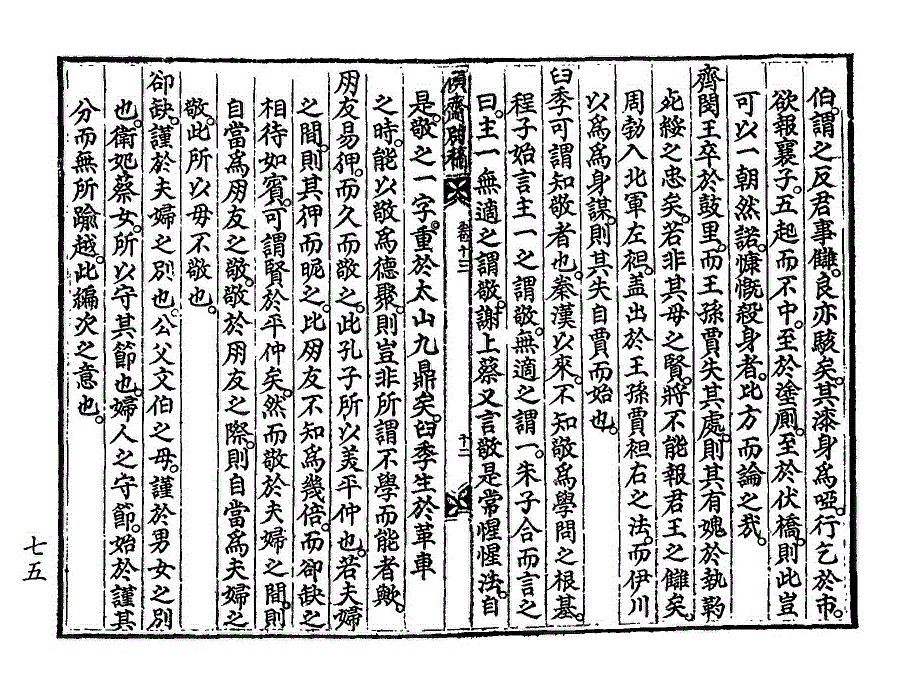 伯。谓之反君事雠。良亦骇矣。其漆身为哑。行乞于市。欲报襄子。五起而不中。至于涂厕。至于伏桥。则此岂可以一朝然诺。慷慨杀身者。比方而论之哉。
伯。谓之反君事雠。良亦骇矣。其漆身为哑。行乞于市。欲报襄子。五起而不中。至于涂厕。至于伏桥。则此岂可以一朝然诺。慷慨杀身者。比方而论之哉。齐闵王卒于鼓里。而王孙贾失其处。则其有愧于执靮死绥之忠矣。若非其母之贤。将不能报君王之雠矣。周勃入北军左袒。盖出于王孙贾袒右之法。而伊川以为为身谋。则其失自贾而始也。
臼季可谓知敬者也。秦汉以来。不知敬为学问之根基。程子始言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子合而言之曰。主一无适之谓敬。谢上蔡又言敬是常惺惺法。自是。敬之一字。重于太山九鼎矣。臼季生于革车▣▣(相争)之时。能以敬为德聚。则岂非所谓不学而能者欤。
朋友易狎。而久而敬之。此孔子所以美平仲也。若夫妇之间。则其狎而昵之。比朋友不知为几倍。而却缺之相待如宾。可谓贤于平仲矣。然而敬于夫妇之间。则自当为朋友之敬。敬于朋友之际。则自当为夫妇之敬。此所以毋不敬也。
却缺。谨于夫妇之别也。公父文伯之母。谨于男女之别也。卫妃,蔡女。所以守其节也。妇人之守节。始于谨其分而无所踰越。此编次之意也。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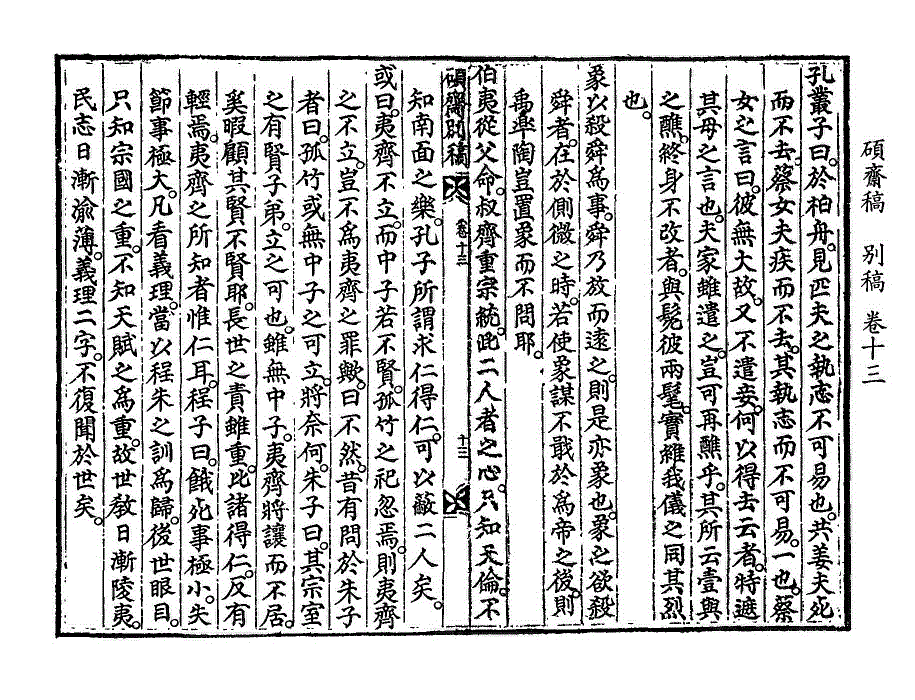 孔丛子曰。于柏舟。见匹夫之执志不可易也。共姜夫死而不去。蔡女夫疾而不去。其执志而不可易。一也。蔡女之言曰。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云者。特遮其母之言也。夫家虽遣之。岂可再醮乎。其所云壹与之醮。终身不改者。与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同其烈也。
孔丛子曰。于柏舟。见匹夫之执志不可易也。共姜夫死而不去。蔡女夫疾而不去。其执志而不可易。一也。蔡女之言曰。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云者。特遮其母之言也。夫家虽遣之。岂可再醮乎。其所云壹与之醮。终身不改者。与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同其烈也。象以杀舜为事。舜乃放而远之。则是亦象也。象之欲杀舜者。在于侧微之时。若使象谋不戢于为帝之后。则禹,皋陶岂置象而不问耶。
伯夷从父命。叔齐重宗统。此二人者之心。只知天伦。不知南面之乐。孔子所谓求仁得仁。可以蔽二人矣。
或曰。夷齐不立。而中子若不贤。孤竹之祀忽焉。则夷齐之不立。岂不为夷齐之罪欤。曰不然。昔有问于朱子者曰。孤竹或无中子之可立。将奈何。朱子曰。其宗室之有贤子弟。立之可也。虽无中子。夷齐将让而不居。奚暇顾其贤不贤耶。长世之责虽重。比诸得仁。反有轻焉。夷齐之所知者惟仁耳。程子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凡看义理。当以程朱之训为归。后世眼目。只知宗国之重。不知天赋之为重。故世教日渐陵夷。民志日渐渝薄。义理二字。不复闻于世矣。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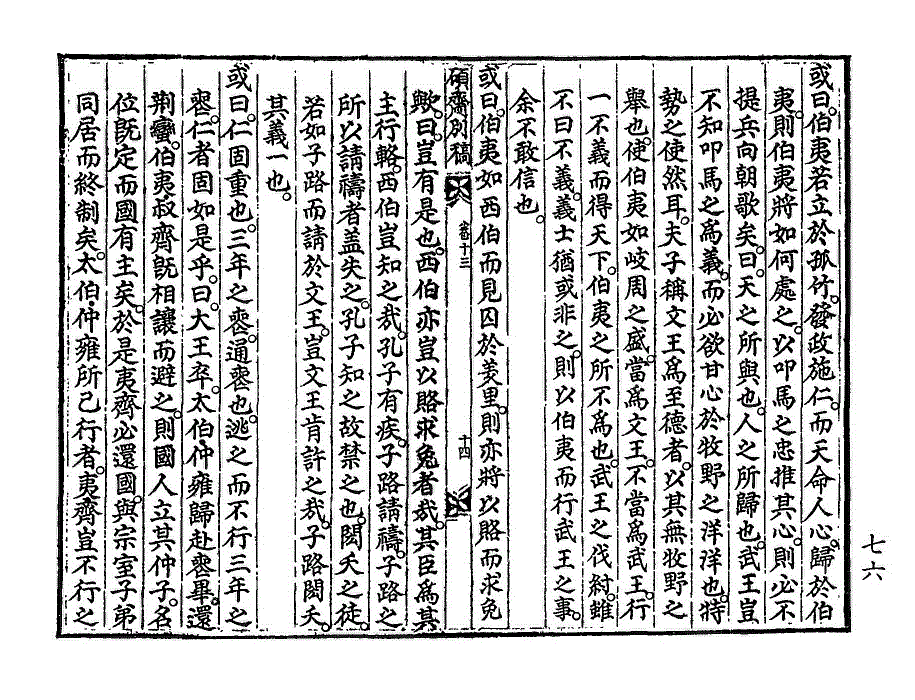 或曰。伯夷若立于孤竹。发政施仁。而天命人心。归于伯夷。则伯夷将如何处之。以叩马之忠推其心。则必不提兵向朝歌矣。曰。天之所与也。人之所归也。武王岂不知叩马之为义。而必欲甘心于牧野之洋洋也。特势之使然耳。夫子称文王为至德者。以其无牧野之举也。使伯夷如岐周之盛。当为文王。不当为武王。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伯夷之所不为也。武王之伐纣。虽不曰不义。义士犹或非之。则以伯夷而行武王之事。余不敢信也。
或曰。伯夷若立于孤竹。发政施仁。而天命人心。归于伯夷。则伯夷将如何处之。以叩马之忠推其心。则必不提兵向朝歌矣。曰。天之所与也。人之所归也。武王岂不知叩马之为义。而必欲甘心于牧野之洋洋也。特势之使然耳。夫子称文王为至德者。以其无牧野之举也。使伯夷如岐周之盛。当为文王。不当为武王。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伯夷之所不为也。武王之伐纣。虽不曰不义。义士犹或非之。则以伯夷而行武王之事。余不敢信也。或曰。伯夷如西伯而见囚于羑里。则亦将以赂而求免欤。曰。岂有是也。西伯亦岂以赂求免者哉。其臣为其主行辂。西伯岂知之哉。孔子有疾。子路请祷。子路之所以请祷者盖失之。孔子知之故禁之也。闳夭之徒。若如子路而请于文王。岂文王肯许之哉。子路闳夭。其义一也。
或曰。仁固重也。三年之丧。通丧也。逃之而不行三年之丧。仁者固如是乎。曰。大王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伯夷,叔齐既相让而避之。则国人立其仲子。名位既定而国有主矣。于是夷齐必还国。与宗室子弟同居而终制矣。太伯,仲雍所已行者。夷,齐岂不行之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7H 页
 哉。
哉。或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而避纣而居北海。往依于西伯。则有若臣事二君者然矣。曰。伯夷何尝臣事于西伯哉。西伯养之以大老。执爵执酳。祝哽祝噎。有如师弟子之礼矣。伯夷之归于西伯。以其善养老也。虽尧舜复生。伯夷非其君则不事。或曰。然则太公亦不臣事于西伯欤。曰。西伯之养太公亦如伯夷。有若伊尹之于汤。汤之不为天子也。辄受学于伊尹。及伐夏之后始臣之。太公为伊尹。伯夷不为太公。
或曰。夷齐若有叩马之意。何不谏于纣而俾悛其恶也。曰。有言责然后谏。伯夷,叔齐。不过海滨之一老人耳。安得以谏之哉。身不出则言亦不出。以夷,齐之贤。岂或犯圣人之攸戒耶。
或曰。武王之观兵孟津也。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伯夷如君于孤竹则将奈何。曰。不但不往。将布告天下以讨武王。而人必无应之者。以国毙焉已矣。不以群后躬助于周庙之祭也审矣。
或曰。崇侯之谮西伯。如祖伊之意。在商固忠臣也。如使伯夷为孤竹之君而事纣。则当如崇侯之为欤。曰。不然。不匡纣之恶。而惟以杀西伯为计。则范增之欲杀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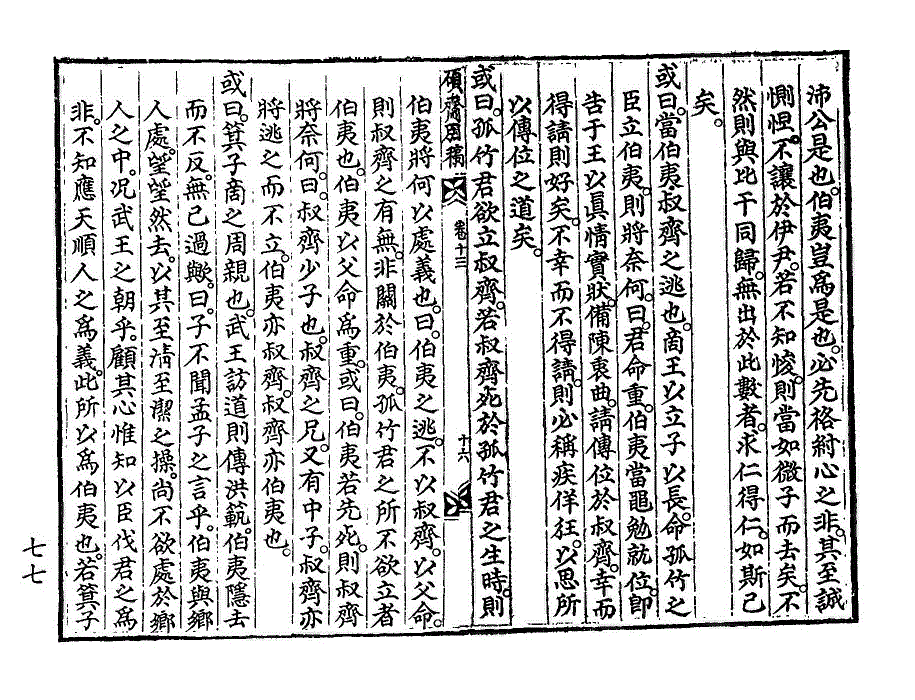 沛公是也。伯夷岂为是也。必先格纣心之非。其至诚恻怛。不让于伊尹。若不知悛。则当如微子而去矣。不然则与比干同归。无出于此数者。求仁得仁。如斯已矣。
沛公是也。伯夷岂为是也。必先格纣心之非。其至诚恻怛。不让于伊尹。若不知悛。则当如微子而去矣。不然则与比干同归。无出于此数者。求仁得仁。如斯已矣。或曰。当伯夷,叔齐之逃也。商王以立子以长。命孤竹之臣立伯夷。则将奈何。曰。君命重。伯夷当黾勉就位。即告于王以真情实状。备陈衷曲。请传位于叔齐。幸而得请则好矣。不幸而不得请。则必称疾佯狂。以思所以传位之道矣。
或曰。孤竹君欲立叔齐。若叔齐死于孤竹君之生时。则伯夷将何以处义也。曰。伯夷之逃。不以叔齐。以父命。则叔齐之有无。非关于伯夷。孤竹君之所不欲立者伯夷也。伯夷以父命为重。或曰。伯夷若先死。则叔齐将奈何。曰。叔齐少子也。叔齐之兄。又有中子。叔齐亦将逃之而不立。伯夷亦叔齐。叔齐亦伯夷也。
或曰。箕子商之周亲也。武王访道则传洪范。伯夷隐去而不反。无已过欤。曰。子不闻孟子之言乎。伯夷与乡人处。望望然去。以其至清至洁之操。尚不欲处于乡人之中。况武王之朝乎。顾其心惟知以臣伐君之为非。不知应天顺人之为义。此所以为伯夷也。若箕子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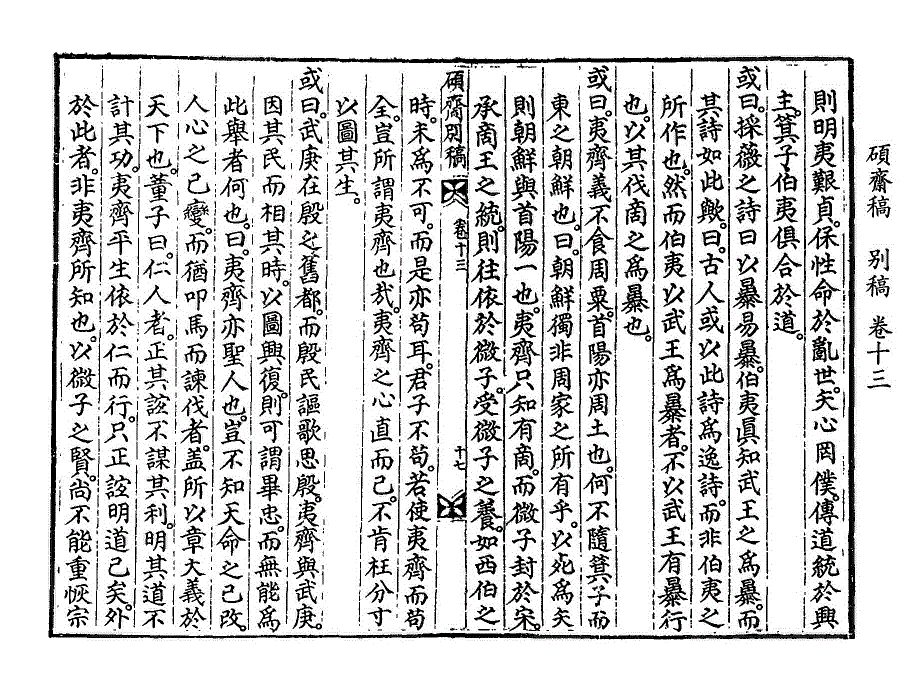 则明夷艰贞。保性命于乱世。矢心罔仆。传道统于兴主。箕子,伯夷俱合于道。
则明夷艰贞。保性命于乱世。矢心罔仆。传道统于兴主。箕子,伯夷俱合于道。或曰。采薇之诗曰以㬥易㬥。伯夷真知武王之为㬥。而其诗如此欤。曰。古人或以此诗为逸诗。而非伯夷之所作也。然而伯夷以武王为㬥者。不以武王有㬥行也。以其伐商之为㬥也。
或曰。夷齐义不食周粟。首阳亦周土也。何不随箕子而东之朝鲜也。曰。朝鲜独非周家之所有乎。以死为矢则朝鲜与首阳一也。夷齐只知有商。而微子封于宋。承商王之统。则往依于微子。受微子之养。如西伯之时。未为不可。而是亦苟耳。君子不苟。若使夷齐而苟全。岂所谓夷齐也哉。夷齐之心直而已。不肯枉分寸以图其生。
或曰。武庚在殷之旧都。而殷民讴歌思殷。夷齐与武庚。因其民而相其时。以图兴复。则可谓毕忠。而无能为此举者何也。曰。夷齐亦圣人也。岂不知天命之已改。人心之已变。而犹叩马而谏伐者。盖所以章大义于天下也。蕫子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夷齐平生依于仁而行。只正谊明道已矣。外于此者。非夷齐所知也。以微子之贤。尚不能重恢宗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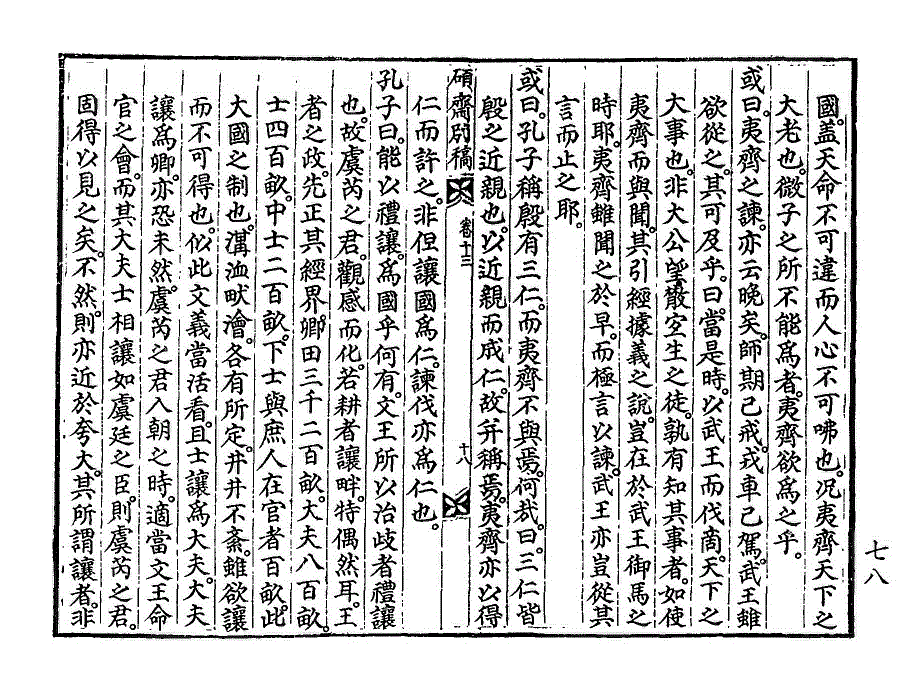 国。盖天命不可违而人心不可咈也。况夷齐天下之大老也。微子之所不能为者。夷齐欲为之乎。
国。盖天命不可违而人心不可咈也。况夷齐天下之大老也。微子之所不能为者。夷齐欲为之乎。或曰。夷齐之谏。亦云晚矣。师期已戒。戎车已驾。武王虽欲从之。其可及乎。曰。当是时。以武王而伐商。天下之大事也。非大公望,散宜生之徒。孰有知其事者。如使夷齐而与闻。其引经据义之说。岂在于武王御马之时耶。夷齐虽闻之于早。而极言以谏。武王亦岂从其言而止之耶。
或曰。孔子称殷有三仁。而夷齐不与焉。何哉。曰。三仁皆殷之近亲也。以近亲而成仁。故并称焉。夷齐亦以得仁而许之。非但让国为仁。谏伐亦为仁也。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文王所以治歧者礼让也。故虞芮之君。观感而化。若耕者让畔。特偶然耳。王者之政。先正其经界。卿田三千二百亩。大夫八百亩。士四百亩。中士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百亩。此大国之制也。沟洫畎浍。各有所定。井井不紊。虽欲让而不可得也。似此文义当活看。且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亦恐未然。虞芮之君入朝之时。适当文王命官之会。而其大夫士相让如虞廷之臣。则虞芮之君。固得以见之矣。不然。则亦近于夸大。其所谓让者。非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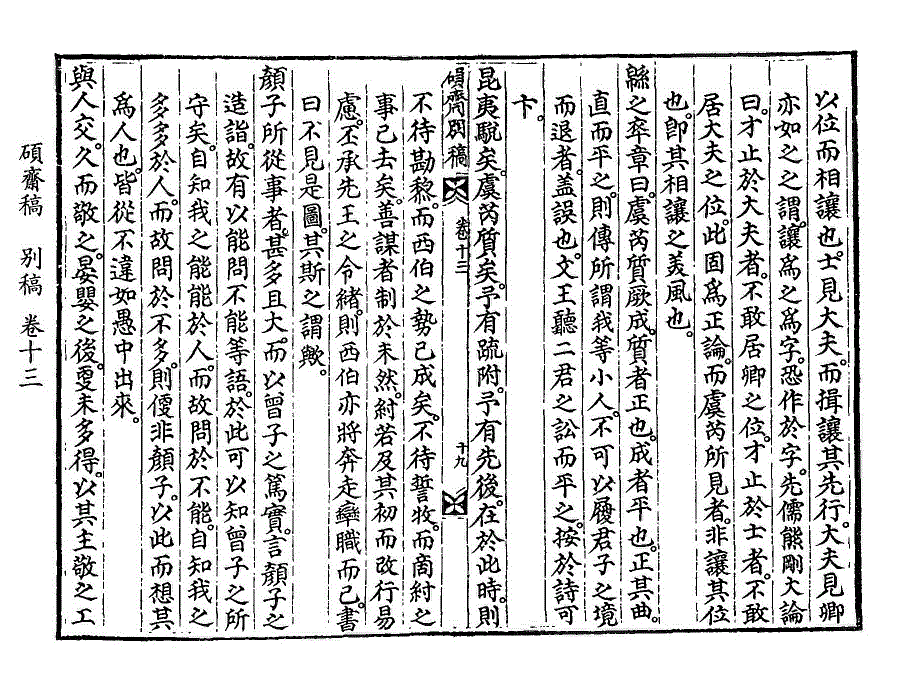 以位而相让也。士见大夫。而揖让其先行。大夫见卿亦如之之谓。让为之为字。恐作于字。先儒熊刚大论曰。才止于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才止于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此固为正论。而虞芮所见者。非让其位也。即其相让之美风也。
以位而相让也。士见大夫。而揖让其先行。大夫见卿亦如之之谓。让为之为字。恐作于字。先儒熊刚大论曰。才止于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才止于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此固为正论。而虞芮所见者。非让其位也。即其相让之美风也。绵之卒章曰。虞芮质厥成。质者正也。成者平也。正其曲。直而平之。则传所谓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而退者。盖误也。文王听二君之讼而平之。按于诗可卞。
昆夷駾矣。虞芮质矣。予有疏附。予有先后。在于此时。则不待勘黎。而西伯之势已成矣。不待誓牧。而商纣之事已去矣。善谋者制于未然。纣若及其初而改行易虑。丕承先王之令绪。则西伯亦将奔走率职而已。书曰不见是图。其斯之谓欤。
颜子所从事者。甚多且大。而以曾子之笃实。言颜子之造诣。故有以能问不能等语。于此可以知曾子之所守矣。自知我之能能于人。而故问于不能。自知我之多多于人。而故问于不多。则便非颜子。以此而想其为人也。皆从不违如愚中出来。
与人交。久而敬之。晏婴之后。更未多得。以其主敬之工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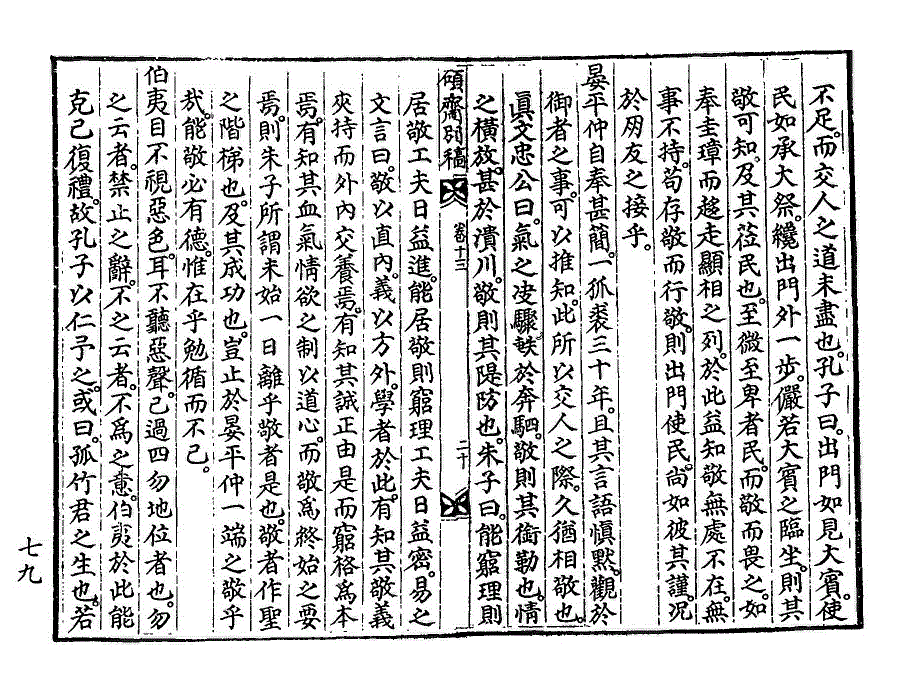 不足。而交人之道未尽也。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才出门外一步。俨若大宾之临坐。则其敬可知。及其莅民也。至微至卑者民。而敬而畏之。如奉圭璋而趍走显相之列。于此益知敬无处不在。无事不持。苟存敬而行敬。则出门使民。尚如彼其谨。况于朋友之接乎。
不足。而交人之道未尽也。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才出门外一步。俨若大宾之临坐。则其敬可知。及其莅民也。至微至卑者民。而敬而畏之。如奉圭璋而趍走显相之列。于此益知敬无处不在。无事不持。苟存敬而行敬。则出门使民。尚如彼其谨。况于朋友之接乎。晏平仲自奉甚简。一狐裘三十年。且其言语慎默。观于御者之事。可以推知。此所以交人之际。久犹相敬也。真文忠公曰。气之决骤。轶于奔驷。敬则其衔勒也。情之横放。甚于溃川。敬则其堤防也。朱子曰。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易之文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学者于此。有知其敬义夹持而外内交养焉。有知其诚正由是而穷格为本焉。有知其血气情欲之制以道心。而敬为终始之要焉。则朱子所谓未始一日离乎敬者是也。敬者作圣之阶梯也。及其成功也。岂止于晏平仲一端之敬乎哉。能敬必有德。惟在乎勉循而不已。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已过四勿地位者也。勿之云者。禁止之辞。不之云者。不为之意。伯夷于此能克己复礼。故孔子以仁予之。或曰。孤竹君之生也。若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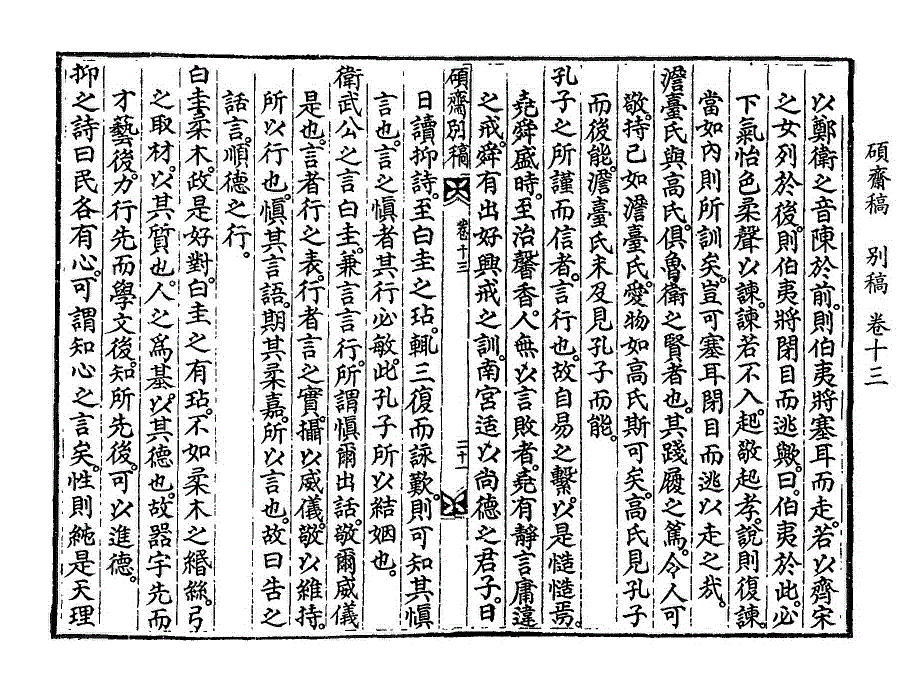 以郑卫之音陈于前。则伯夷将塞耳而走。若以齐宋之女列于后。则伯夷将闭目而逃欤。曰。伯夷于此。必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当如内则所训矣。岂可塞耳闭目而逃以走之哉。
以郑卫之音陈于前。则伯夷将塞耳而走。若以齐宋之女列于后。则伯夷将闭目而逃欤。曰。伯夷于此。必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当如内则所训矣。岂可塞耳闭目而逃以走之哉。澹台氏与高氏。俱鲁,卫之贤者也。其践履之笃。令人可敬。持己如澹台氏。爱物如高氏斯可矣。高氏见孔子而后能。澹台氏未及见孔子而能。
孔子之所谨而信者。言行也。故自易之系。以是慥慥焉。尧舜盛时。至治馨香。人无以言败者。尧有静言庸违之戒。舜有出好兴戒之训。南宫适以尚德之君子。日日读抑诗。至白圭之玷。辄三复而咏叹。则可知其慎言也。言之慎者其行必敏。此孔子所以结姻也。
卫武公之言白圭。兼言言行。所谓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是也。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实。摄以威仪。敬以维持。所以行也。慎其言语。期其柔嘉。所以言也。故曰告之话言。顺德之行。
白圭,柔木。政是好对。白圭之有玷。不如柔木之缗丝。弓之取材。以其质也。人之为基。以其德也。故器宇先而才艺后。力行先而学文后。知所先后。可以进德。
抑之诗曰民各有心。可谓知心之言矣。性则纯是天理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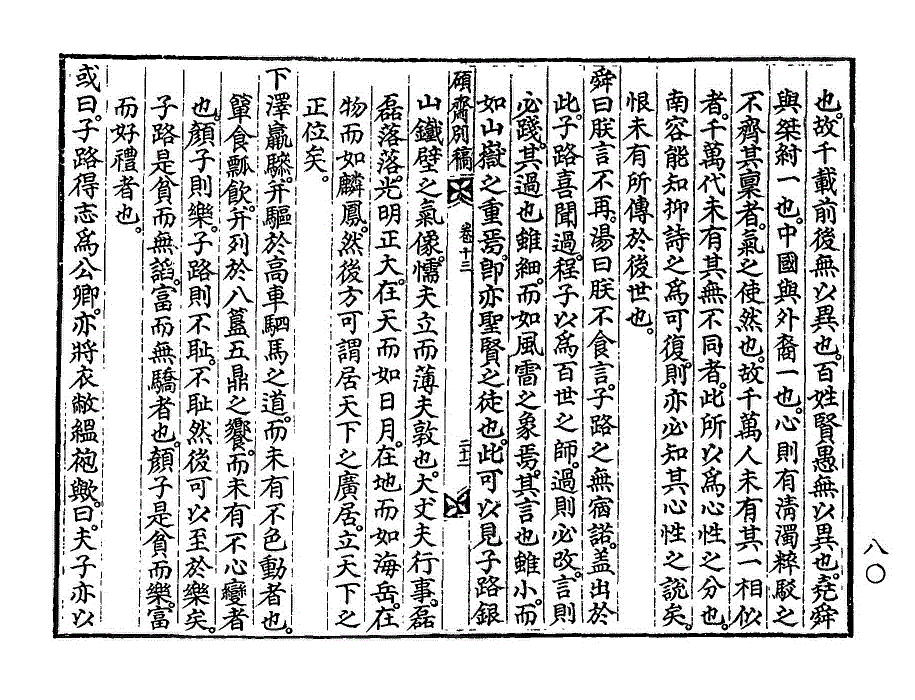 也。故千载前后无以异也。百姓贤愚无以异也。尧舜与桀纣一也。中国与外裔一也。心则有清浊粹驳之不齐其禀者。气之使然也。故千万人未有其一相似者。千万代未有其无不同者。此所以为心性之分也。南容能知抑诗之为可复。则亦必知其心性之说矣。恨未有所传于后世也。
也。故千载前后无以异也。百姓贤愚无以异也。尧舜与桀纣一也。中国与外裔一也。心则有清浊粹驳之不齐其禀者。气之使然也。故千万人未有其一相似者。千万代未有其无不同者。此所以为心性之分也。南容能知抑诗之为可复。则亦必知其心性之说矣。恨未有所传于后世也。舜曰朕言不再。汤曰朕不食言。子路之无宿诺。盖出于此。子路喜闻过。程子以为百世之师。过则必改。言则必践。其过也虽细。而如风䨓之象焉。其言也虽小。而如山岳之重焉。即亦圣贤之徒也。此可以见子路银山铁壁之气像。懦夫立而薄夫敦也。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光明正大。在天而如日月。在地而如海岳。在物而如麟凤。然后方可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矣。
下泽羸骖。并驱于高车驷马之道。而未有不色动者也。箪食瓢饮。并列于八簋五鼎之飨。而未有不心变者也。颜子则乐。子路则不耻。不耻然后可以至于乐矣。子路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者也。颜子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或曰。子路得志为公卿。亦将衣敝缊袍欤。曰。夫子亦以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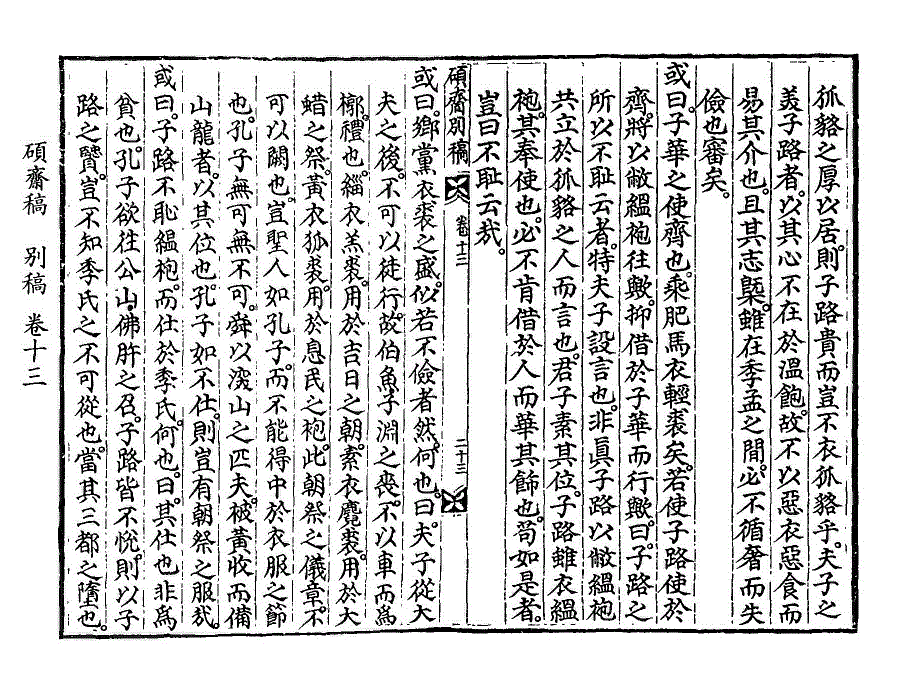 狐貉之厚以居。则子路贵而岂不衣狐貉乎。夫子之美子路者。以其心不在于温饱。故不以恶衣恶食而易其介也。且其志槩。虽在季孟之间。必不循奢而失俭也审矣。
狐貉之厚以居。则子路贵而岂不衣狐貉乎。夫子之美子路者。以其心不在于温饱。故不以恶衣恶食而易其介也。且其志槩。虽在季孟之间。必不循奢而失俭也审矣。或曰。子华之使齐也。乘肥马衣轻裘矣。若使子路使于齐。将以敝缊袍往欤。抑借于子华而行欤。曰。子路之所以不耻云者。特夫子设言也。非真子路以敝缊袍共立于狐貉之人而言也。君子素其位。子路虽衣缊袍。其奉使也。必不肯借于人而华其饰也。苟如是者。岂曰不耻云哉。
或曰。乡党衣裘之盛。似若不俭者然。何也。曰。夫子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故伯鱼,子渊之丧。不以车而为椁。礼也。缁衣羔裘。用于吉日之朝。素衣麑裘。用于大蜡之祭。黄衣狐裘。用于息民之袍。此朝祭之仪章。不可以阙也。岂圣人如孔子。而不能得中于衣服之节也。孔子无可无不可。舜以深山之匹夫。被黄收而备山龙者。以其位也。孔子如不仕。则岂有朝祭之服哉。
或曰。子路不耻缊袍。而仕于季氏。何也。曰。其仕也非为贫也。孔子欲往公山,佛㬳(一作肸)之召。子路皆不悦。则以子路之贤。岂不知季氏之不可从也。当其三都之堕也。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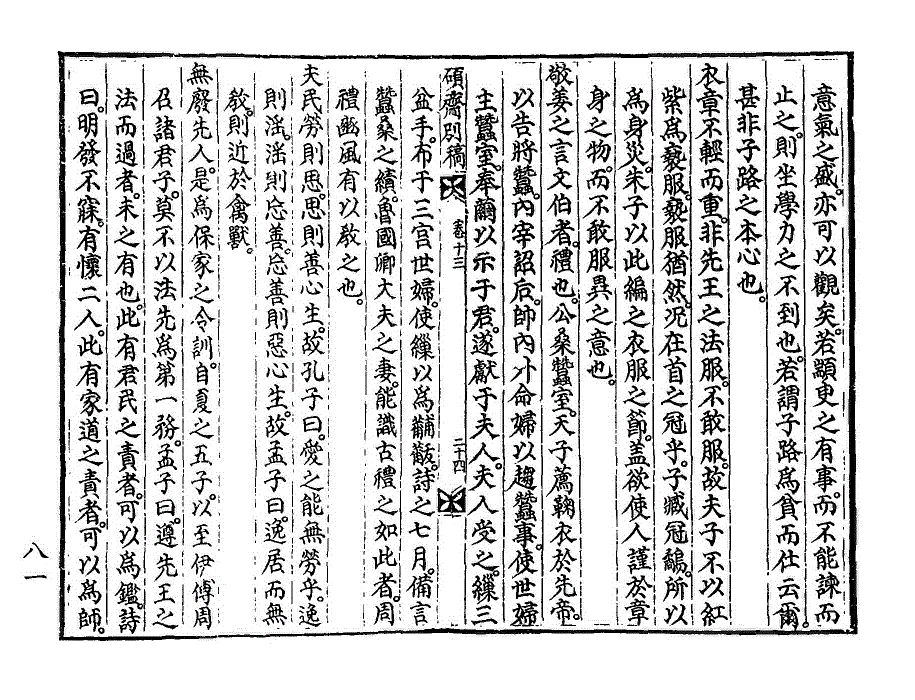 意气之盛。亦可以观矣。若颛臾之有事。而不能谏而止之。则坐学力之不到也。若谓子路为贫而仕云尔。甚非子路之本心也。
意气之盛。亦可以观矣。若颛臾之有事。而不能谏而止之。则坐学力之不到也。若谓子路为贫而仕云尔。甚非子路之本心也。衣章不轻而重。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故夫子不以红紫为亵服。亵服犹然。况在首之冠乎。子臧冠鹬。所以为身灾。朱子以此编之衣服之节。盖欲使人谨于章身之物。而不敢服异之意也。
敬姜之言文伯者。礼也。公桑蚕室。天子荐鞠衣于先帝。以告将蚕。内宰诏后。帅内外命妇以趋蚕事。使世妇主蚕室。奉茧以示于君。遂献于夫人。夫人受之。缫三盆手。布于三宫世妇。使缫以为黼黻。诗之七月。备言蚕桑之绩。鲁国卿大夫之妻。能识古礼之如此者。周礼豳风有以教之也。
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故孔子曰。爱之能无劳乎。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故孟子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无废先人。是为保家之令训。自夏之五子。以至伊傅周召诸君子。莫不以法先为第一务。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此有君民之责者。可以为鉴。诗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此有家道之责者。可以为师。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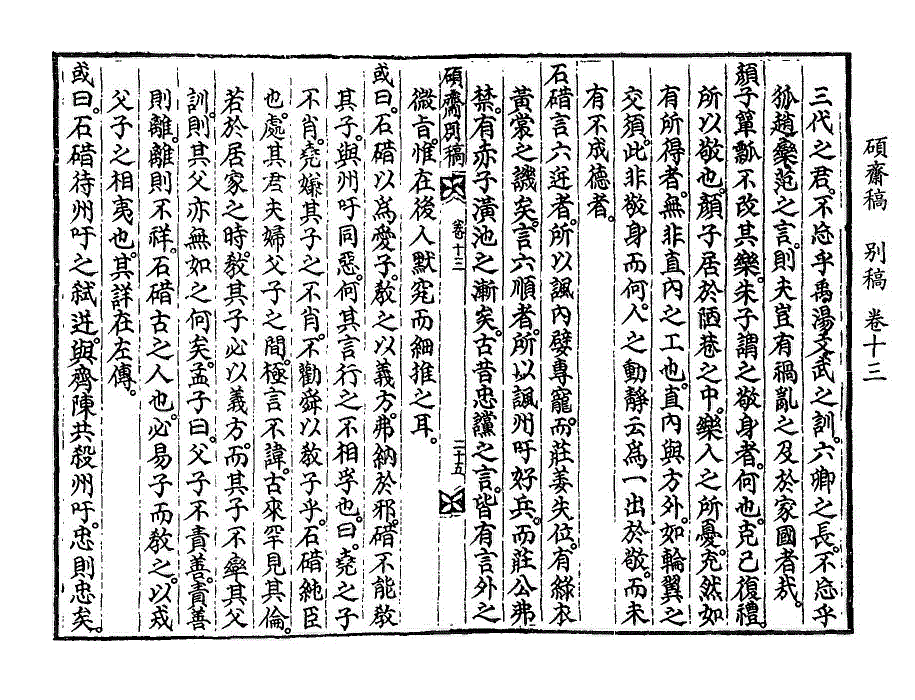 三代之君。不忘乎禹,汤,文,武之训。六卿之长。不忘乎狐,赵,栾,范之言。则夫岂有祸乱之及于家国者哉。
三代之君。不忘乎禹,汤,文,武之训。六卿之长。不忘乎狐,赵,栾,范之言。则夫岂有祸乱之及于家国者哉。颜子箪瓢不改其乐。朱子谓之敬身者。何也。克己复礼。所以敬也。颜子居于陋巷之中。乐人之所忧。充然如有所得者。无非直内之工也。直内与方外。如轮翼之交须。此非敬身而何。人之动静云为一出于敬。而未有不成德者。
石碏言六逆者。所以讽内嬖专宠。而庄姜失位。有绿衣黄裳之讥矣。言六顺者。所以讽州吁好兵。而庄公弗禁。有赤子潢池之渐矣。古昔忠谠之言。皆有言外之微旨。惟在后人默究而细推之耳。
或曰。石碏以为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碏不能教其子。与州吁同恶。何其言行之不相孚也。曰。尧之子不肖。尧嫌其子之不肖。不劝舜以教子乎。石碏纯臣也。处其君夫妇父子之间。极言不讳。古来罕见其伦。若于居家之时。教其子必以义方。而其子不率其父训。则其父亦无如之何矣。孟子曰。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石碏古之人也。必易子而教之。以戒父子之相夷也。其详在左传。
或曰。石碏待州吁之弑逆。与齐陈共杀州吁。忠则忠矣。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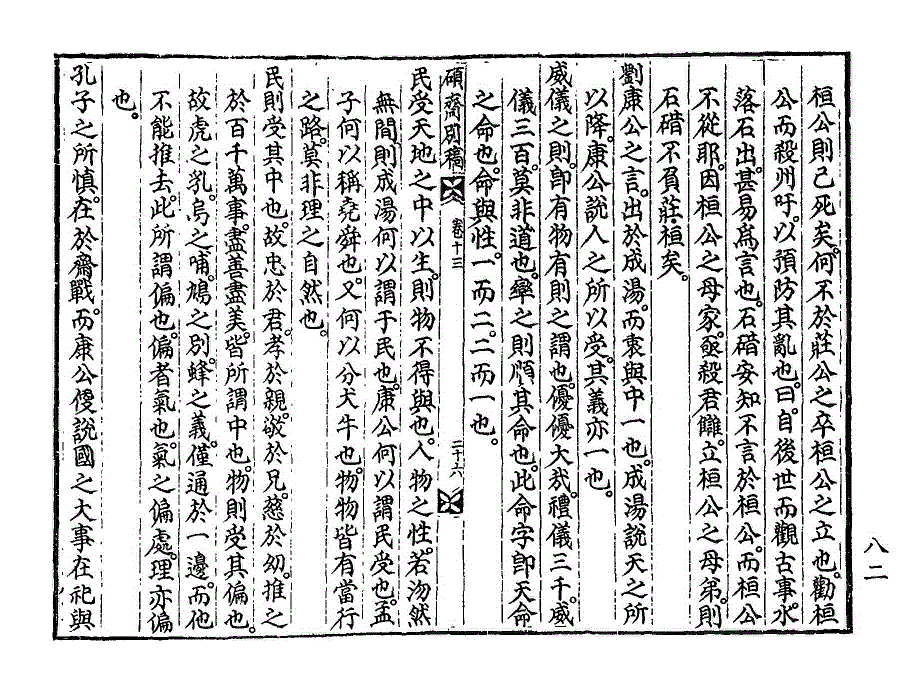 桓公则已死矣。何不于庄公之卒桓公之立也。劝桓公而杀州吁。以预防其乱也。曰。自后世而观古事。水落石出。甚易为言也。石碏安知不言于桓公。而桓公不从耶。因桓公之母家。亟杀君雠。立桓公之母弟。则石碏不负庄,桓矣。
桓公则已死矣。何不于庄公之卒桓公之立也。劝桓公而杀州吁。以预防其乱也。曰。自后世而观古事。水落石出。甚易为言也。石碏安知不言于桓公。而桓公不从耶。因桓公之母家。亟杀君雠。立桓公之母弟。则石碏不负庄,桓矣。刘康公之言。出于成汤。而衷与中一也。成汤说天之所以降。康公说人之所以受。其义亦一也。
威仪之则。即有物有则之谓也。优优大哉。礼仪三千。威仪三百。莫非道也。率之则顺其命也。此命字即天命之命也。命与性。一而二。二而一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则物不得与也。人物之性。若沕然无间。则成汤何以谓于民也。康公何以谓民受也。孟子何以称尧舜也。又何以分犬牛也。物物皆有当行之路。莫非理之自然也。
民则受其中也。故忠于君。孝于亲。敬于兄。慈于幼。推之于百千万事。尽善尽美。皆所谓中也。物则受其偏也。故虎之乳。乌之哺。鸠之别。蜂之义。仅通于一边。而他不能推去。此所谓偏也。偏者气也。气之偏处。理亦偏也。
孔子之所慎。在于斋战。而康公便说国之大事在祀与
硕斋别稿卷之十三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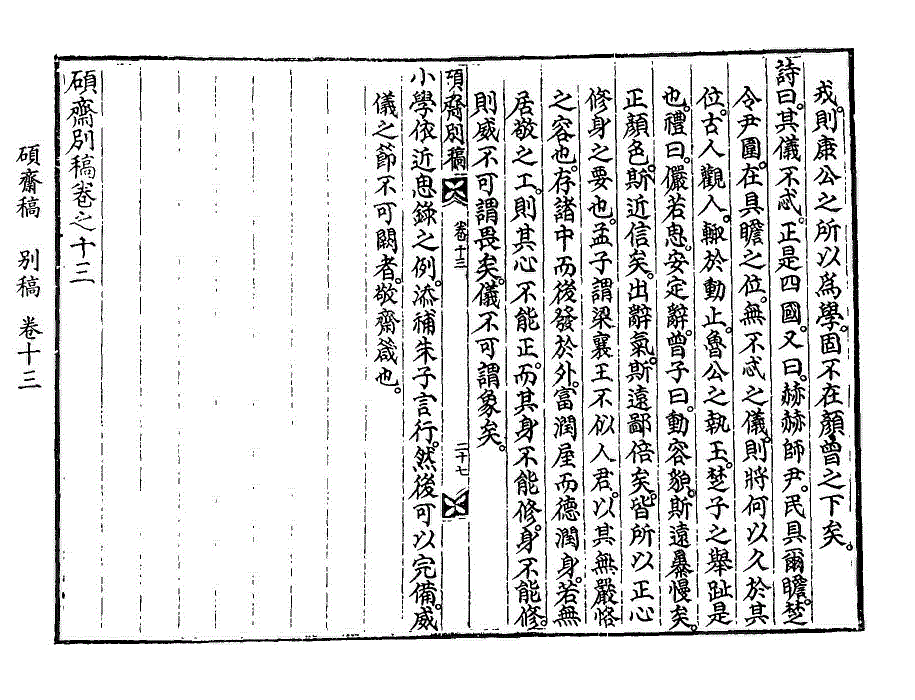 戎。则康公之所以为学。固不在颜,曾之下矣。
戎。则康公之所以为学。固不在颜,曾之下矣。诗曰。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又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楚令尹围。在具瞻之位。无不忒之仪。则将何以久于其位。古人观人。辄于动止。鲁公之执玉。楚子之举趾是也。礼曰。俨若思。安定辞。曾子曰。动容貌。斯远㬥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皆所以正心修身之要也。孟子谓梁襄王不似人君。以其无严恪之容也。存诸中而后发于外。富润屋而德润身。若无居敬之工。则其心不能正。而其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则威不可谓畏矣。仪不可谓象矣。
小学依近思录之例。添补朱子言行。然后可以完备。威仪之节不可阙者。敬斋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