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十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尚书精英。尽在于二典。自三谟以下。皆不出二典之外。而夏书四篇。又是绝调。殷周之所未见者。文以代降。不其然欤。既读虞夏之书。仍始汤誓。以及其下。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尚书精英。尽在于二典。自三谟以下。皆不出二典之外。而夏书四篇。又是绝调。殷周之所未见者。文以代降。不其然欤。既读虞夏之书。仍始汤誓。以及其下。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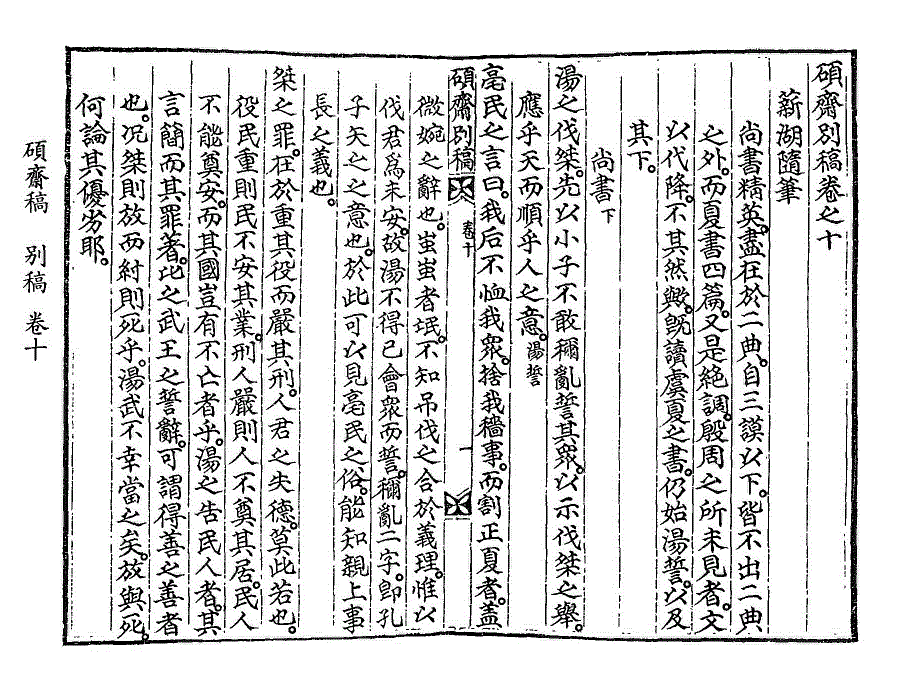 尚书[下]
尚书[下]汤之伐桀。先以小子不敢称乱誓其众。以示伐桀之举。应乎天而顺乎人之意。(汤誓)
亳民之言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者。盖微婉之辞也。蚩蚩者氓。不知吊伐之合于义理。惟以伐君为未安。故汤不得已会众而誓。称乱二字。即孔子矢之之意也。于此可以见亳民之俗。能知亲上事长之义也。
桀之罪。在于重其役而严其刑。人君之失德。莫此若也。役民重则民不安其业。刑人严则人不奠其居。民人不能奠安。而其国岂有不亡者乎。汤之告民人者。其言简而其罪著。比之武王之誓辞。可谓得善之善者也。况桀则放而纣则死乎。汤武不幸当之矣。放与死。何论其优劣耶。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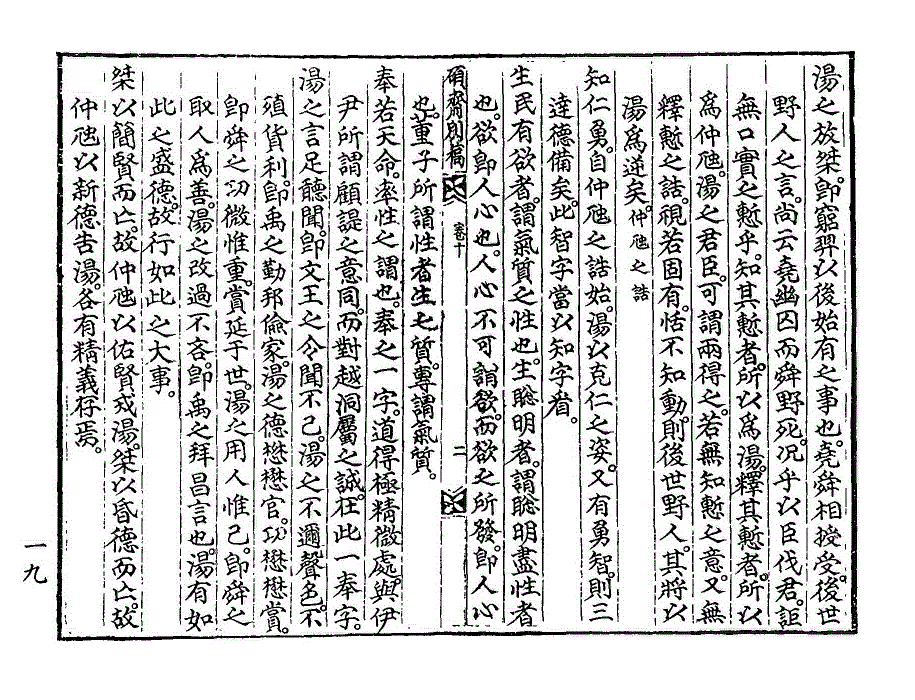 汤之放桀。即穷羿以后始有之事也。尧舜相授受。后世野人之言。尚云尧幽囚而舜野死。况乎以臣伐君。讵无口实之惭乎。知其惭者。所以为汤。释其惭者。所以为仲虺。汤之君臣。可谓两得之。若无知惭之意。又无释惭之诰。视若固有。恬不知动。则后世野人。其将以汤为逆矣。(仲虺之诰)
汤之放桀。即穷羿以后始有之事也。尧舜相授受。后世野人之言。尚云尧幽囚而舜野死。况乎以臣伐君。讵无口实之惭乎。知其惭者。所以为汤。释其惭者。所以为仲虺。汤之君臣。可谓两得之。若无知惭之意。又无释惭之诰。视若固有。恬不知动。则后世野人。其将以汤为逆矣。(仲虺之诰)知仁勇。自仲虺之诰始。汤以克仁之姿。又有勇智。则三达德备矣。此智字当以知字看。
生民有欲者。谓气质之性也。生聪明者。谓聪明尽性者也。欲即人心也。人心不可谓欲。而欲之所发。即人心也。董子所谓性者生之质。专谓气质。
奉若天命。率性之谓也。奉之一字。道得极精微处。与伊尹所谓顾諟之意同。而对越洞属之诚。在此一奉字。
汤之言足听闻。即文王之令闻不已。汤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即禹之勤邦俭家。汤之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即舜之功微惟重。赏延于世。汤之用人惟己。即舜之取人为善。汤之改过不吝。即禹之拜昌言也。汤有如此之盛德。故行如此之大事。
桀以简贤而亡。故仲虺以佑贤戒汤。桀以昏德而亡。故仲虺以新德告汤。各有精义存焉。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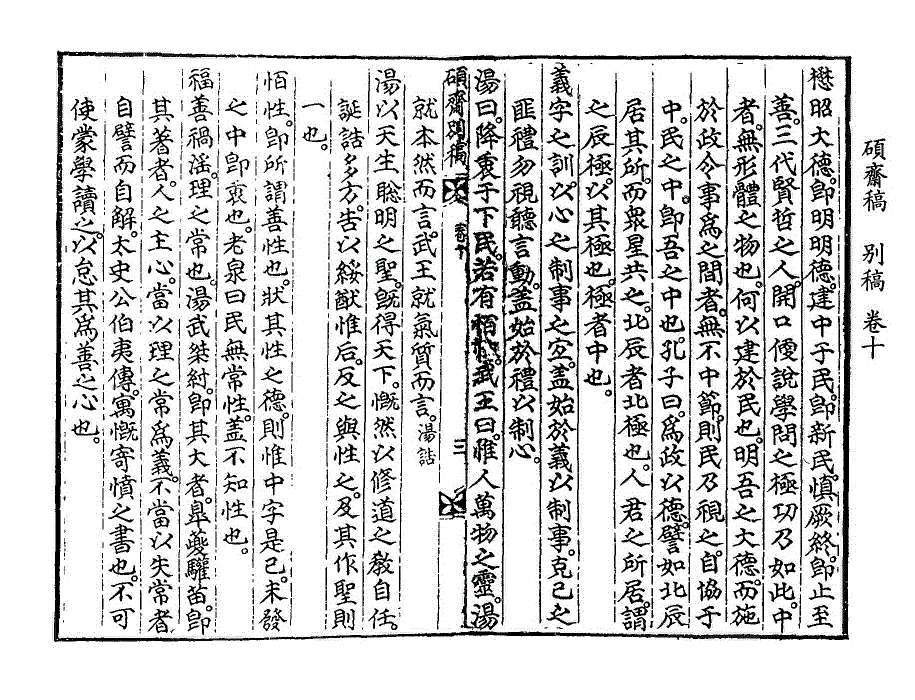 懋昭大德。即明明德。建中于民。即新民。慎厥终。即止至善。三代贤哲之人。开口便说学问之极功乃如此。中者。无形体之物也。何以建于民也。明吾之大德。而施于政令事为之间者。无不中节。则民乃视之。自协于中。民之中。即吾之中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者北极也。人君之所居。谓之辰极。以其极也。极者中也。
懋昭大德。即明明德。建中于民。即新民。慎厥终。即止至善。三代贤哲之人。开口便说学问之极功乃如此。中者。无形体之物也。何以建于民也。明吾之大德。而施于政令事为之间者。无不中节。则民乃视之。自协于中。民之中。即吾之中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者北极也。人君之所居。谓之辰极。以其极也。极者中也。义字之训。以心之制事之宜。盖始于义以制事。克己之匪礼勿视听言动。盖始于礼以制心。
汤曰。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武王曰。惟人万物之灵。汤就本然而言。武王就气质而言。(汤诰)
汤以天生聪明之圣。既得天下。慨然以修道之教自任。诞诰多方。告以绥猷惟后。反之与性之。及其作圣则一也。
恒性。即所谓善性也。状其性之德。则惟中字是已。未发之中即衷也。老泉曰民无常性。盖不知性也。
福善祸淫。理之常也。汤武桀纣。即其大者。皋夔驩苗。即其著者。人之主心。当以理之常为义。不当以失常者自譬而自解。太史公伯夷传。寓慨寄愤之书也。不可使蒙学读之。以怠其为善之心也。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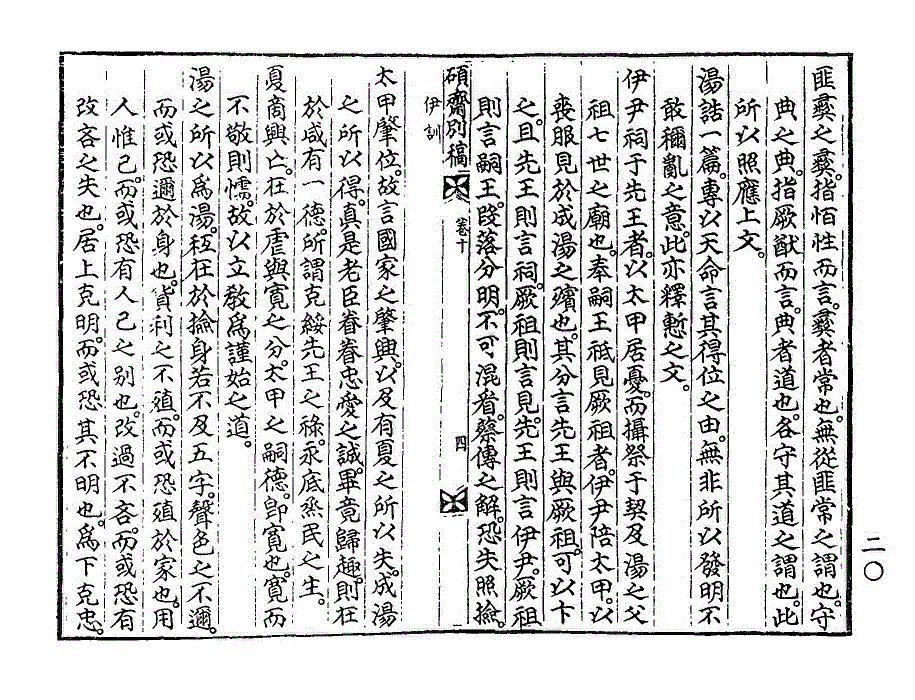 匪彝之彝。指恒性而言。彝者常也。无从匪常之谓也。守典之典。指厥猷而言。典者道也。各守其道之谓也。此所以照应上文。
匪彝之彝。指恒性而言。彝者常也。无从匪常之谓也。守典之典。指厥猷而言。典者道也。各守其道之谓也。此所以照应上文。汤诰一篇。专以天命言其得位之由。无非所以发明不敢称乱之意。此亦释惭之文。
伊尹祠于先王者。以太甲居忧。而摄祭于契及汤之父祖七世之庙也。奉嗣王祗见厥祖者。伊尹陪太甲。以丧服见于成汤之殡也。其分言先王与厥祖。可以卞之。且先王则言祠。厥祖则言见。先王则言伊尹。厥祖则言嗣王。段落分明。不可混看。蔡传之解。恐失照捡。(伊训)
太甲肇位。故言国家之肇兴。以及有夏之所以失。成汤之所以得。真是老臣眷眷忠爱之诚。毕竟归趣。则在于咸有一德。所谓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夏商兴亡。在于虐与宽之分。太甲之嗣德。即宽也。宽而不敬则懦。故以立教为谨始之道。
汤之所以为汤。秪在于捡身若不及五字。声色之不迩。而或恐迩于身也。货利之不殖。而或恐殖于家也。用人惟己。而或恐有人己之别也。改过不吝。而或恐有改吝之失也。居上克明。而或恐其不明也。为下克忠。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1H 页
 而或恐其不忠也。日新又日新。若有歉焉。如颜子之克己。曾子之省身。皆从此做出来。而为圣为贤。即其功效也。若捡身之方。从诚意而做得。诚意之工。以弗欺为主。
而或恐其不忠也。日新又日新。若有歉焉。如颜子之克己。曾子之省身。皆从此做出来。而为圣为贤。即其功效也。若捡身之方。从诚意而做得。诚意之工。以弗欺为主。官刑三风。侮圣言居三。孔子言三畏。亦居其一。孔子之言。似或引此为用。而圣人言语。往往有不谋而同者。是一团天理。
曰舞曰酣曰歌。巫风之目。曰货曰色曰游畋。淫风之目。曰侮曰逆曰远曰比。乱风之目。合以为十愆。而官刑之文。押韵成章。亦诗体也。
顾諟明命。即成汤日新日跻之所由成也。常目在是。造次不离。故其新也其跻也。维日不足。而天降大命。所以监其明德也。(太甲)
上章言承绪。下章言忝祖。只在于祗之一字。祗则可以承其绪。不祗则不可以承绪。绪之不承。是谓忝祖。汤与伊尹一生用工。在于敬。自顾諟日新。罔不以敬为主。
伊尹乃言曰者。即史笔也。太甲惟庸。罔念闻。故伊尹以为我既作书而告之。王不采纳。则我岂可无言。遂进言以谏。史氏以乃言曰三字。表以出之。盖所以志王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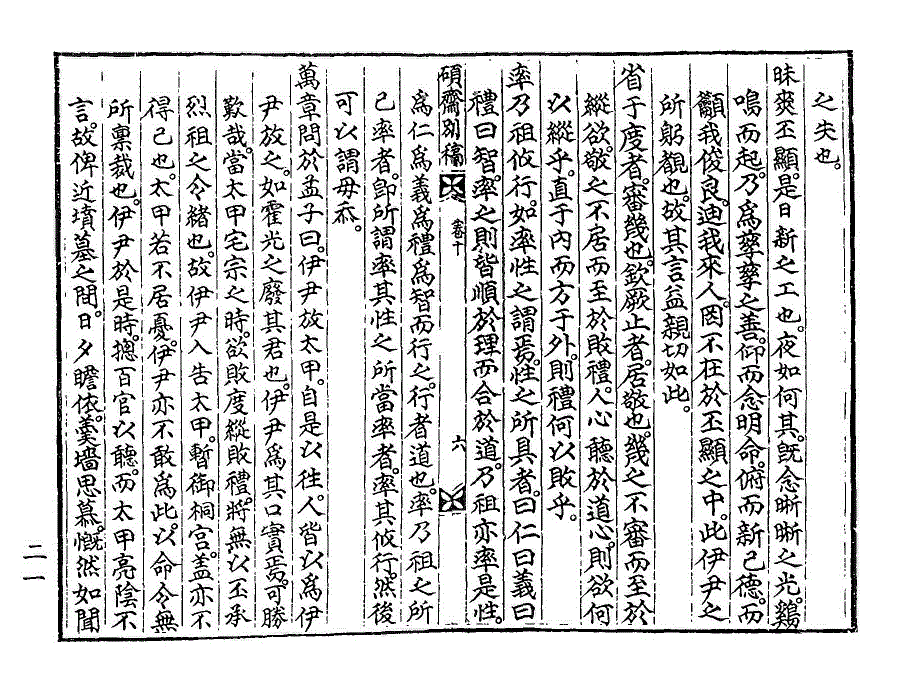 之失也。
之失也。昧爽丕显。是日新之工也。夜如何其。既念晢晢之光。鸡鸣而起。乃为孳孳之善。仰而念明命。俯而新己德。而吁我俊良。迪我来人。罔不在于丕显之中。此伊尹之所躬睹也。故其言益亲切如此。
省于度者。审几也。钦厥止者。居敬也。几之不审而至于纵欲。敬之不居而至于败礼。人心听于道心。则欲何以纵乎。直于内而方于外。则礼何以败乎。
率乃祖攸行。如率性之谓焉。性之所具者。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率之则皆顺于理而合于道。乃祖亦率是性。为仁为义为礼为智而行之。行者道也。率乃祖之所已率者。即所谓率其性之所当率者。率其攸行。然后可以谓毋忝。
万章问于孟子曰。伊尹放太甲。自是以往。人皆以为伊尹放之。如霍光之废其君也。伊尹为其口实焉。可胜叹哉。当太甲宅宗之时。欲败度纵败礼。将无以丕承烈祖之令绪也。故伊尹入告太甲。暂御桐宫。盖亦不得已也。太甲若不居忧。伊尹亦不敢为此。以命令无所禀裁也。伊尹于是时。总百官以听。而太甲亮阴不言。故俾近坟墓之间。日夕瞻依。羹墙思慕。慨然如闻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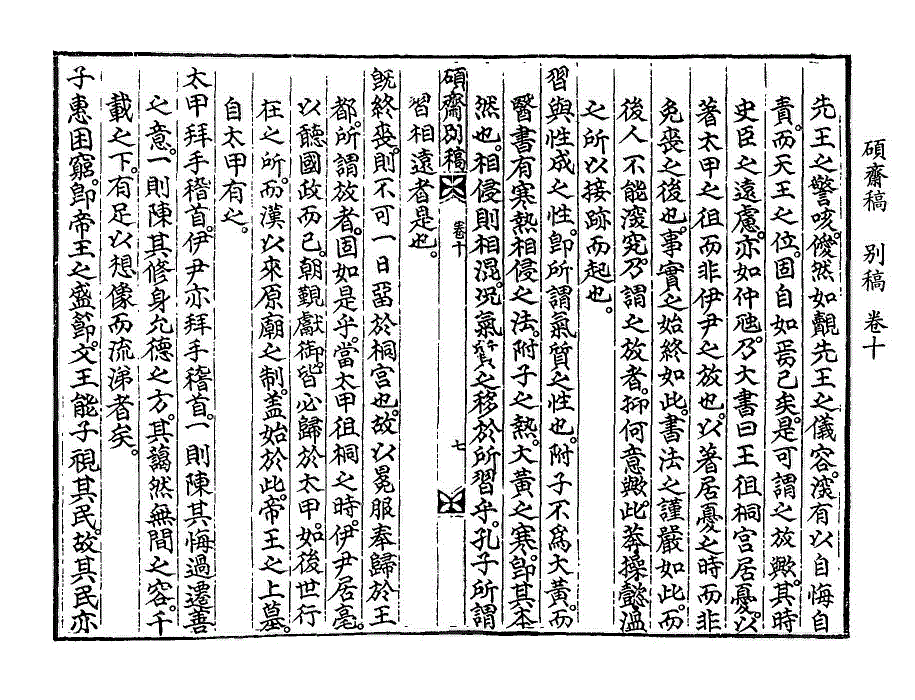 先王之警咳。僾然如觌先王之仪容。深有以自悔自责。而天王之位。固自如焉已矣。是可谓之放欤。其时史臣之远虑。亦如仲虺。乃大书曰王徂桐宫居忧。以著太甲之徂而非伊尹之放也。以著居忧之时而非免丧之后也。事实之始终如此。书法之谨严如此。而后人不能深究。乃谓之放者。抑何意欤。此莽,操,懿,温之所以接迹而起也。
先王之警咳。僾然如觌先王之仪容。深有以自悔自责。而天王之位。固自如焉已矣。是可谓之放欤。其时史臣之远虑。亦如仲虺。乃大书曰王徂桐宫居忧。以著太甲之徂而非伊尹之放也。以著居忧之时而非免丧之后也。事实之始终如此。书法之谨严如此。而后人不能深究。乃谓之放者。抑何意欤。此莽,操,懿,温之所以接迹而起也。习与性成之性。即所谓气质之性也。附子不为大黄。而医书有寒热相侵之法。附子之热。大黄之寒。即其本然也。相侵则相混。况气质之移于所习乎。孔子所谓习相远者是也。
既终丧。则不可一日留于桐宫也。故以冕服奉归于王都。所谓放者。固如是乎。当太甲徂桐之时。伊尹居亳。以听国政而已。朝觐献御。皆必归于太甲。如后世行在之所。而汉以来原庙之制。盖始于此。帝王之上墓。自太甲有之。
太甲拜手稽首。伊尹亦拜手稽首。一则陈其悔过迁善之意。一则陈其修身允德之方。其蔼然无间之容。千载之下。有足以想像而流涕者矣。
子惠困穷。即帝王之盛节。文王能子视其民。故其民亦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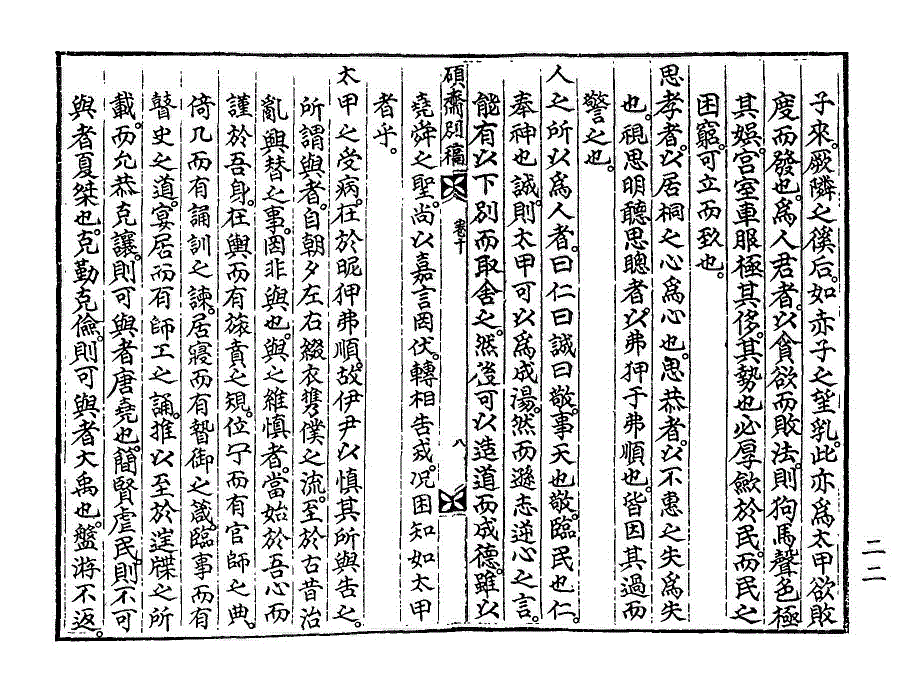 子来。厥邻之徯后。如赤子之望乳。此亦为太甲欲败度而发也。为人君者。以贪欲而败法。则狗马声色极其娱。宫室车服极其侈。其势也必厚敛于民。而民之困穷。可立而致也。
子来。厥邻之徯后。如赤子之望乳。此亦为太甲欲败度而发也。为人君者。以贪欲而败法。则狗马声色极其娱。宫室车服极其侈。其势也必厚敛于民。而民之困穷。可立而致也。思孝者。以居桐之心为心也。思恭者。以不惠之失为失也。视思明听思聪者。以弗狎于弗顺也。皆因其过而警之也。
人之所以为人者。曰仁曰诚曰敬。事天也敬。临民也仁。奉神也诚。则太甲可以为成汤。然而逊志逆心之言。能有以下别而取舍之。然后可以造道而成德。虽以尧舜之圣。尚以嘉言罔伏。转相告戒。况困知如太甲者乎。
太甲之受病。在于昵狎弗顺。故伊尹以慎其所与告之。所谓与者。自朝夕左右缀衣携仆之流。至于古昔治乱兴替之事。罔非与也。与之维慎者。当始于吾心而谨于吾身。在舆而有旅贲之规。位宁而有官师之典。倚几而有诵训之谏。居寝而有亵御之箴。临事而有瞽史之道。宴居而有师工之诵。推以至于𨓏牒之所载。而允恭克让。则可与者唐尧也。简贤虐民。则不可与者夏桀也。克勤克俭。则可与者大禹也。盘游不返。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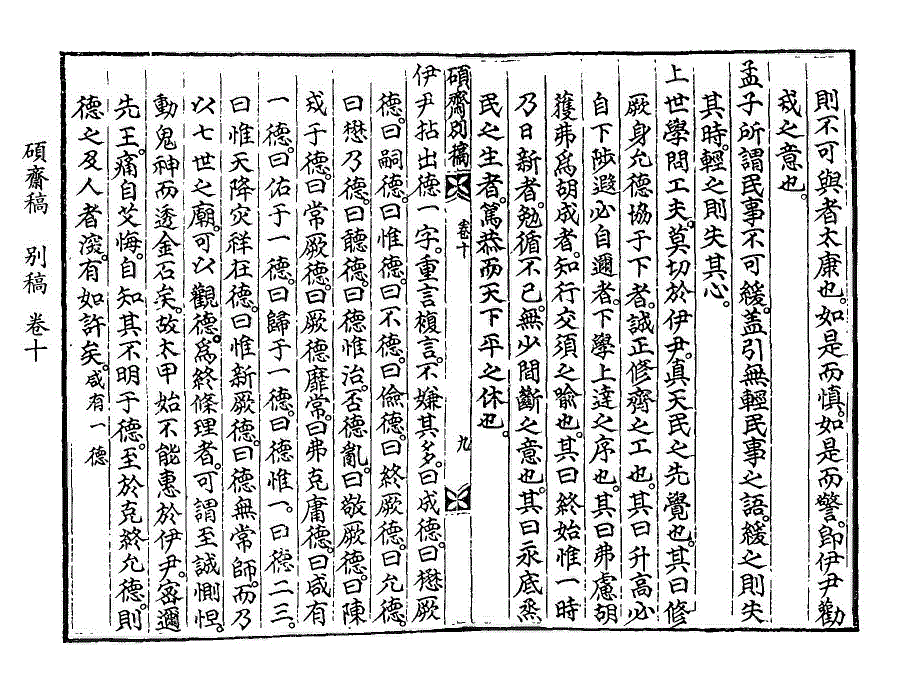 则不可与者太康也。如是而慎。如是而警。即伊尹劝戒之意也。
则不可与者太康也。如是而慎。如是而警。即伊尹劝戒之意也。孟子所谓民事不可缓。盖引无轻民事之语。缓之则失其时。轻之则失其心。
上世学问工夫。莫切于伊尹。真天民之先觉也。其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者。诚正修齐之工也。其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迩者。下学上达之序也。其曰弗虑胡获弗为胡成者。知行交须之喻也。其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者。勉循不已。无少间断之意也。其曰永底烝民之生者。笃恭而天下平之休也。
伊尹拈出德一字。重言复言。不嫌其多。曰成德。曰懋厥德。曰嗣德。曰惟德。曰不德。曰俭德。曰终厥德。曰允德。曰懋乃德。曰听德。曰德惟治。否德乱。曰敬厥德。曰陈戒于德。曰常厥德。曰厥德靡常。曰弗克庸德。曰咸有一德。曰佑于一德。曰归于一德。曰德惟一。曰德二三。曰惟天降灾祥在德。曰惟新厥德。曰德无常师。而乃以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为终条理者。可谓至诚恻怛。动鬼神而透金石矣。故太甲始不能惠于伊尹。密迩先王。痛自艾悔。自知其不明于德。至于克终允德。则德之及人者深。有如许矣。(咸有一德)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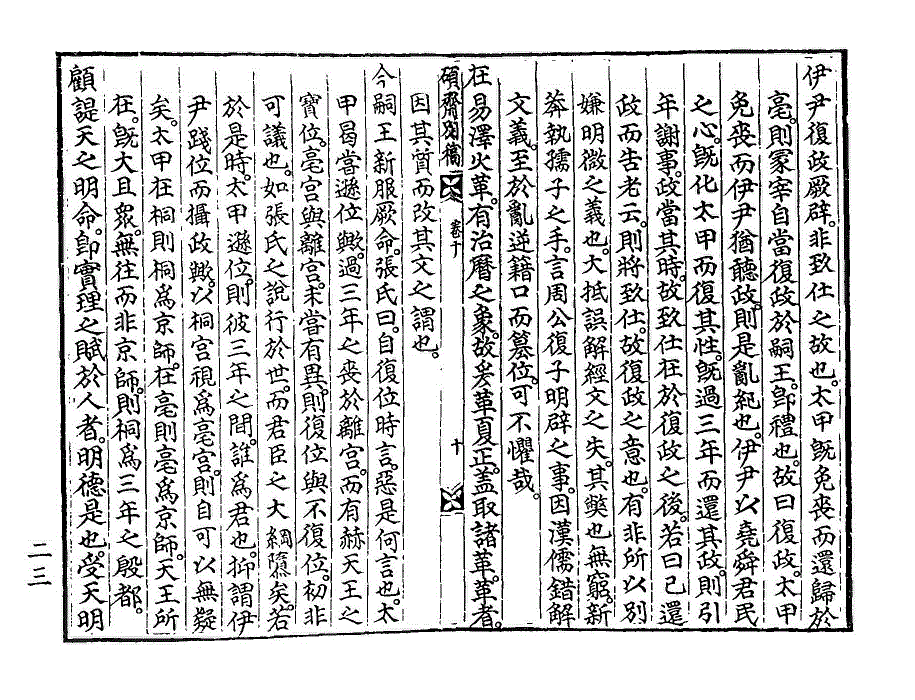 伊尹复政厥辟。非致仕之故也。太甲既免丧而还归于亳。则冢宰自当复政于嗣王。即礼也。故曰复政。太甲免丧而伊尹犹听政。则是乱纪也。伊尹以尧舜君民之心。既化太甲而复其性。既过三年而还其政。则引年谢事。政当其时。故致仕在于复政之后。若曰已还政而告老云。则将致仕。故复政之意也。有非所以别嫌明微之义也。大抵误解经文之失。其弊也无穷。新莽执孺子之手。言周公复子明辟之事。因汉儒错解文义。至于乱逆籍口而篡位。可不惧哉。
伊尹复政厥辟。非致仕之故也。太甲既免丧而还归于亳。则冢宰自当复政于嗣王。即礼也。故曰复政。太甲免丧而伊尹犹听政。则是乱纪也。伊尹以尧舜君民之心。既化太甲而复其性。既过三年而还其政。则引年谢事。政当其时。故致仕在于复政之后。若曰已还政而告老云。则将致仕。故复政之意也。有非所以别嫌明微之义也。大抵误解经文之失。其弊也无穷。新莽执孺子之手。言周公复子明辟之事。因汉儒错解文义。至于乱逆籍口而篡位。可不惧哉。在易泽火革。有治历之象。故爰革夏正。盖取诸革。革者。因其质而改其文之谓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张氏曰。自复位时言。恶是何言也。太甲曷尝逊位欤。过三年之丧于离宫。而有赫天王之宝位。亳宫与离宫。未尝有异。则复位与不复位。初非可议也。如张氏之说行于世。而君臣之大纲隳矣。若于是时。太甲逊位。则彼三年之间。谁为君也。抑谓伊尹践位而摄政欤。以桐宫视为亳宫。则自可以无疑矣。太甲在桐则桐为京师。在亳则亳为京师。天王所在。既大且众。无往而非京师。则桐为三年之殷都。
顾諟天之明命。即实理之赋于人者。明德是也。受天明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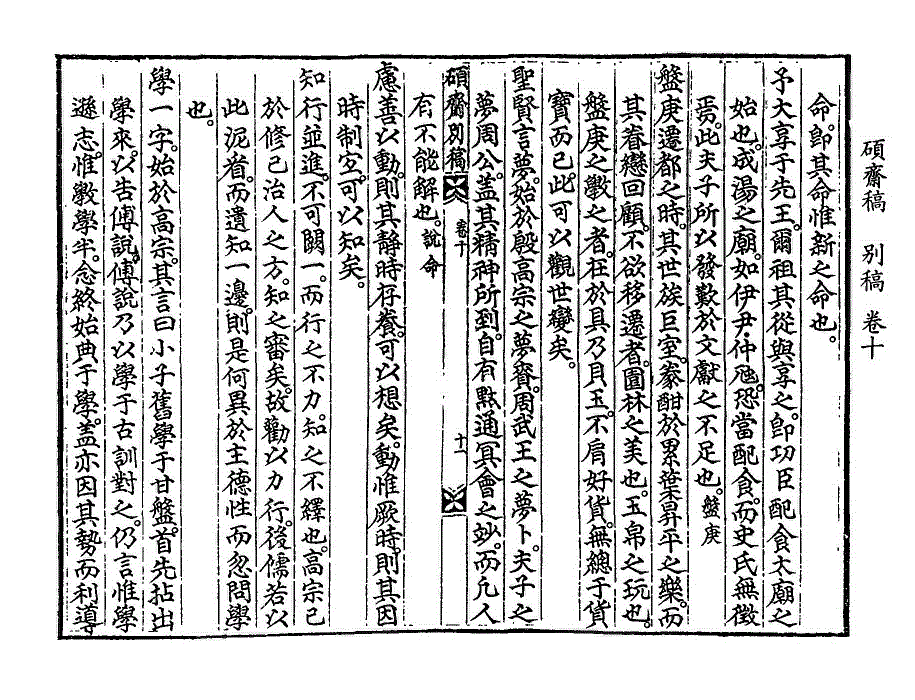 命。即其命惟新之命也。
命。即其命惟新之命也。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即功臣配食太庙之始也。成汤之庙。如伊尹,仲虺。恐当配食。而史氏无徵焉。此夫子所以发叹于文献之不足也。(盘庚)
盘庚迁都之时。其世族巨室。豢酣于累叶升平之乐。而其眷恋回顾。不欲移迁者。园林之美也。玉帛之玩也。盘庚之敩之者。在于具乃贝玉。不肩好货。无总于货宝而已。此可以观世变矣。
圣贤言梦。始于殷高宗之梦赉。周武王之梦卜。夫子之梦周公。盖其精神所到。自有默通冥会之妙。而凡人有不能解也。(说命)
虑善以动。则其静时存养。可以想矣。动惟厥时。则其因时制宜。可以知矣。
知行并进。不可阙一。而行之不力。知之不绎也。高宗已于修己治人之方。知之审矣。故劝以力行。后儒若以此泥看。而遗知一边。则是何异于主德性而忽问学也。
学一字。始于高宗。其言曰小子旧学于甘盘。首先拈出学来。以告傅说。傅说乃以学于古训对之。仍言惟学逊志。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盖亦因其势而利导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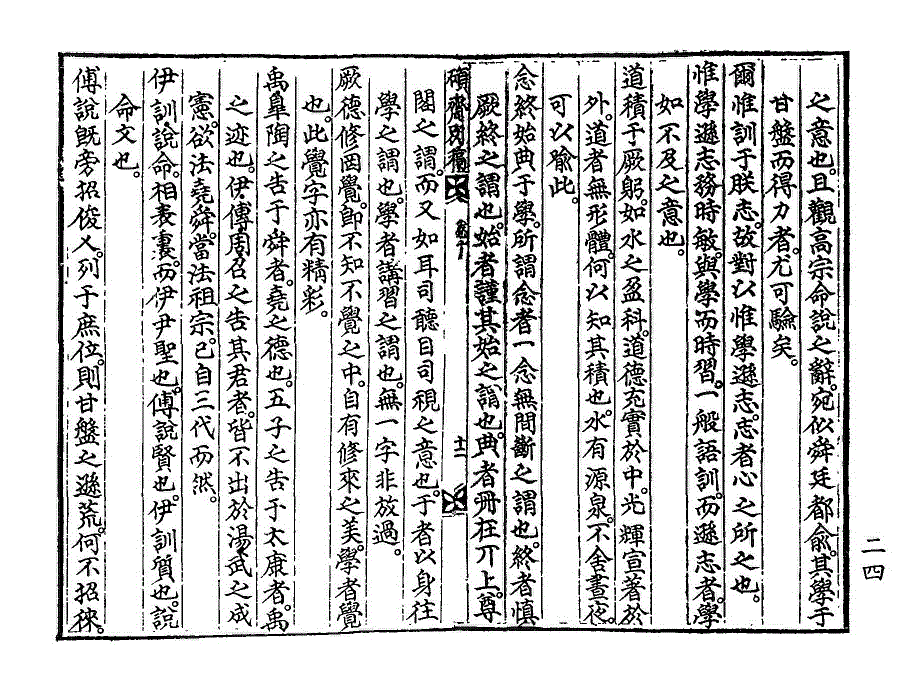 之意也。且观高宗命说之辞。宛似舜廷都俞。其学于甘盘而得力者。尤可验矣。
之意也。且观高宗命说之辞。宛似舜廷都俞。其学于甘盘而得力者。尤可验矣。尔惟训于朕志。故对以惟学逊志。志者心之所之也。
惟学逊志务时敏。与学而时习。一般语训。而逊志者。学如不及之意也。
道积于厥躬。如水之盈科。道德充实于中。光辉宣著于外。道者无形体。何以知其积也。水有源泉。不舍昼夜。可以喻此。
念终始典于学。所谓念者一念无间断之谓也。终者慎厥终之谓也。始者谨其始之谓也。典者册在丌上。尊阁之谓。而又如耳司听目司视之意也。于者以身往学之谓也。学者讲习之谓也。无一字非放过。
厥德修罔觉。即不知不觉之中。自有修来之美。学者觉也。此觉字亦有精彩。
禹,皋陶之告于舜者。尧之德也。五子之告于太康者。禹之迹也。伊,傅,周,召之告其君者。皆不出于汤,武之成宪。欲法尧舜。当法祖宗。已自三代而然。
伊训,说命。相表里。而伊尹圣也。傅说贤也。伊训质也。说命文也。
傅说既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则甘盘之逊荒。何不招徕。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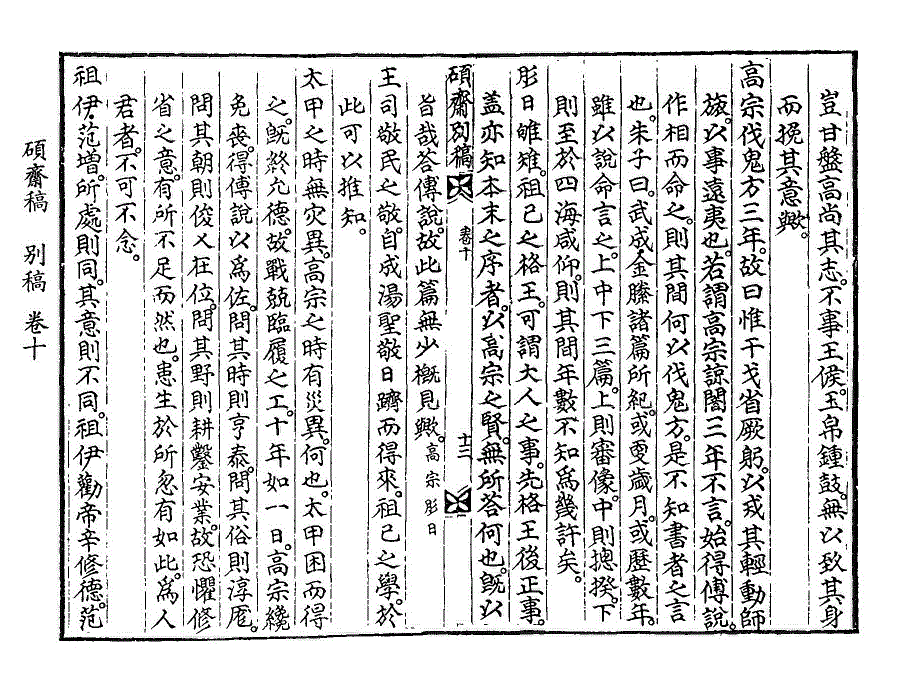 岂甘盘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玉帛钟鼓。无以致其身而挽其意欤。
岂甘盘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玉帛钟鼓。无以致其身而挽其意欤。高宗伐鬼方三年。故曰惟干戈省厥躬。以戒其轻动师旅。以事远夷也。若谓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始得傅说。作相而命之。则其间何以伐鬼方。是不知书者之言也。朱子曰。武成,金縢诸篇所纪。或更岁月。或历数年。虽以说命言之。上中下三篇。上则审像。中则总揆。下则至于四海咸仰。则其间年数不知为几许矣。
肜日雊雉。祖己之格王。可谓大人之事。先格王后正事。盖亦知本末之序者。以高宗之贤。无所答何也。既以旨哉答傅说。故此篇无少概见欤。(高宗肜日)
王司敬民之敬。自成汤圣敬日跻而得来。祖己之学。于此可以推知。
太甲之时无灾异。高宗之时有灾异。何也。太甲困而得之。既终允德。故战兢临履之工。十年如一日。高宗才免丧。得傅说以为佐。问其时则亨泰。问其俗则淳厖。问其朝则俊乂在位。问其野则耕凿安业。故恐惧修省之意。有所不足而然也。患生于所忽有如此。为人君者。不可不念。
祖伊,范增。所处则同。其意则不同。祖伊劝帝辛修德。范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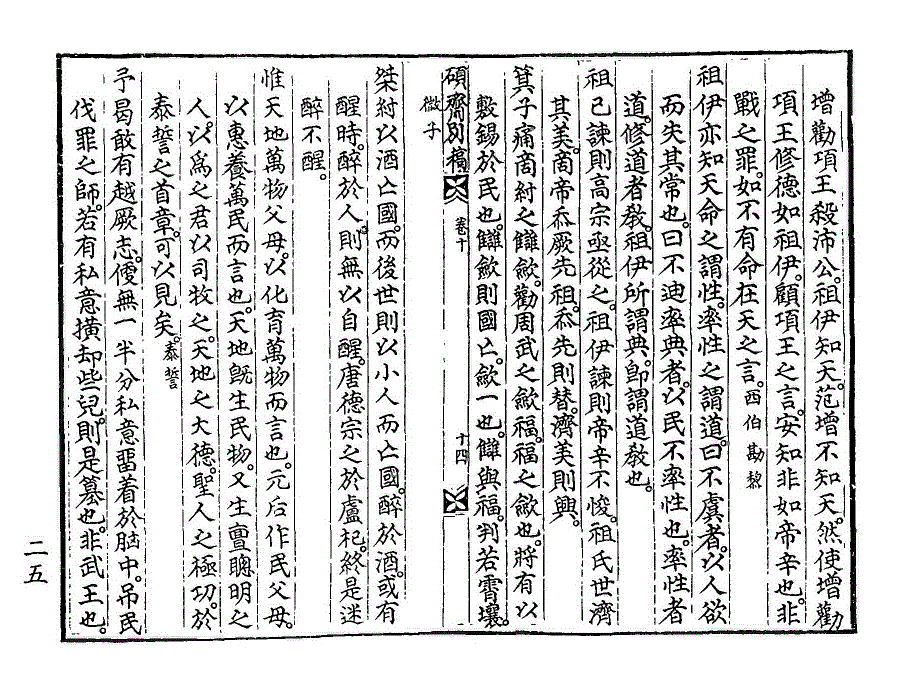 增劝项王杀沛公。祖伊知天。范增不知天。然使增劝项王修德如祖伊。顾项王之言。安知非如帝辛也。非战之罪。如不有命在天之言。(西伯勘黎)
增劝项王杀沛公。祖伊知天。范增不知天。然使增劝项王修德如祖伊。顾项王之言。安知非如帝辛也。非战之罪。如不有命在天之言。(西伯勘黎)祖伊亦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曰不虞者。以人欲而失其常也。曰不迪率典者。以民不率性也。率性者道。修道者教。祖伊所谓典。即谓道教也。
祖己谏则高宗亟从之。祖伊谏则帝辛不悛。祖氏世济其美。商帝忝厥先祖。忝先则替。济美则兴。
箕子痛商纣之雠敛。劝周武之敛福。福之敛也。将有以敷锡于民也。雠敛则国亡。敛一也。雠与福。判若霄壤。(微子)
桀纣以酒亡国。而后世则以小人而亡国。醉于酒。或有醒时。醉于人。则无以自醒。唐德宗之于卢杞。终是迷醉不醒。
惟天地万物父母。以化育万物而言也。元后作民父母。以惠养万民而言也。天地既生民物。又生亶聪明之人。以为之君以司牧之。天地之大德。圣人之极功。于泰誓之首章。可以见矣。(泰誓)
予曷敢有越厥志。便无一半分私意留着于胸中。吊民伐罪之师。若有私意横却些儿。则是篡也。非武王也。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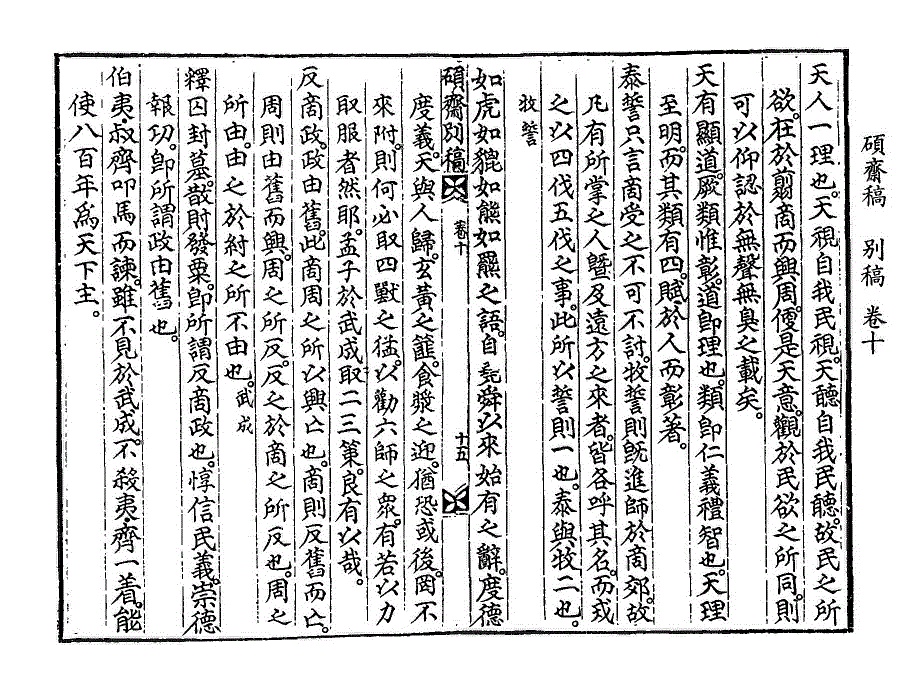 天人一理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民之所欲。在于剪商而兴周。便是天意。观于民欲之所同。则可以仰认于无声无臭之载矣。
天人一理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民之所欲。在于剪商而兴周。便是天意。观于民欲之所同。则可以仰认于无声无臭之载矣。天有显道。厥类惟彰。道即理也。类即仁义礼智也。天理至明。而其类有四。赋于人而彰著。
泰誓只言商受之不可不讨。牧誓则既进师于商郊。故凡有所掌之人暨及远方之来者。皆各呼其名。而戒之以四伐五伐之事。此所以誓则一也。泰与牧二也。(牧誓)
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之语。自尧舜以来始有之辞。度德度义。天与人归。玄黄之篚。食浆之迎。犹恐或后。罔不来附。则何必取四兽之猛。以劝六师之众。有若以力取服者然耶。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良有以哉。
反商政。政由旧。此商周之所以兴亡也。商则反旧而亡。周则由旧而兴。周之所反。反之于商之所反也。周之所由。由之于纣之所不由也。(武成)
释囚封墓。散财发粟。即所谓反商政也。惇信民义。崇德报功。即所谓政由旧也。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虽不见于武成。不杀夷,齐一着。能使八百年为天下主。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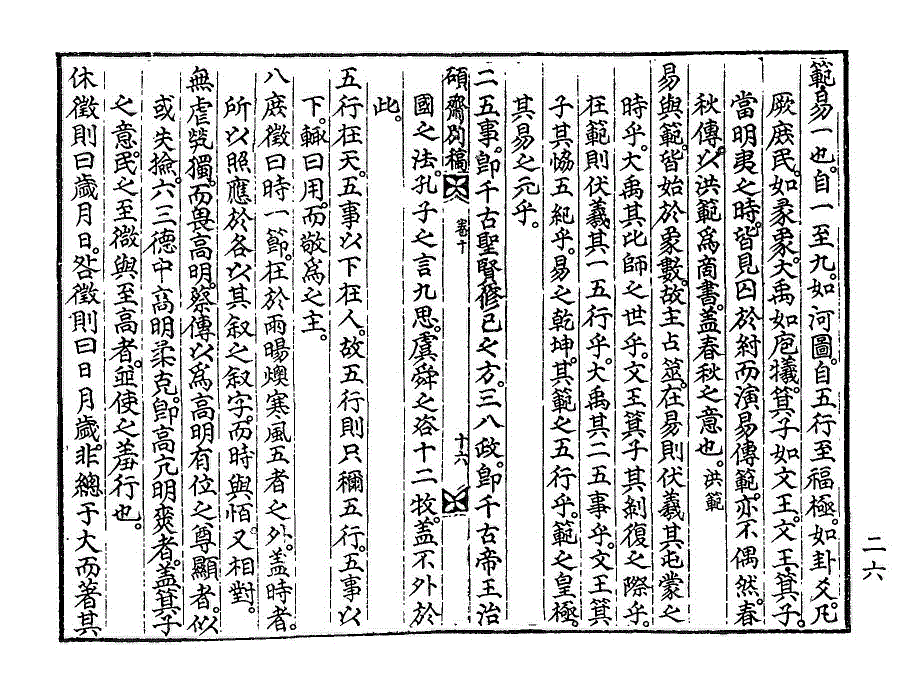 范,易一也。自一至九。如河图。自五行至福极。如卦爻。凡厥庶民。如彖象。大禹如庖牺。箕子如文王。文王,箕子。当明夷之时。皆见囚于纣而演易传范。亦不偶然。春秋传。以洪范为商书。盖春秋之意也。(洪范)
范,易一也。自一至九。如河图。自五行至福极。如卦爻。凡厥庶民。如彖象。大禹如庖牺。箕子如文王。文王,箕子。当明夷之时。皆见囚于纣而演易传范。亦不偶然。春秋传。以洪范为商书。盖春秋之意也。(洪范)易与范。皆始于象数。故主占筮。在易则伏羲其屯蒙之时乎。大禹其比师之世乎。文王箕子其剥复之际乎。在范则伏羲其一五行乎。大禹其二五事乎。文王箕子其协五纪乎。易之乾坤。其范之五行乎。范之皇极。其易之元乎。
二五事。即千古圣贤修己之方。三八政。即千古帝王治国之法。孔子之言九思。虞舜之咨十二牧。盖不外于此。
五行在天。五事以下在人。故五行则只称五行。五事以下。辄曰用。而敬为之主。
八庶徵曰时一节。在于雨旸燠寒风五者之外。盖时者。所以照应于各以其叙之叙字。而时与恒。又相对。
无虐煢独。而畏高明。蔡传以为高明有位之尊显者。似或失捡。六三德中高明柔克。即高亢明爽者。盖箕子之意。民之至微与至高者。并使之羞行也。
休徵则曰岁月日。咎徵则曰日月岁。非总于大而著其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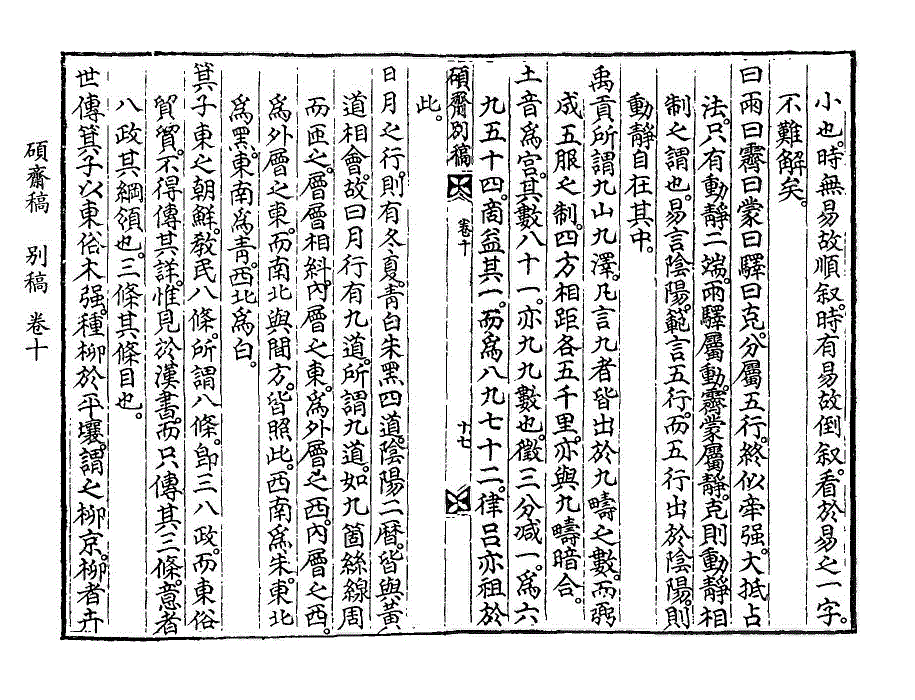 小也。时无易故顺叙。时有易故倒叙。看于易之一字。不难解矣。
小也。时无易故顺叙。时有易故倒叙。看于易之一字。不难解矣。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分属五行。终似牵强。大抵占法。只有动静二端。雨驿属动。霁蒙属静。克则动静相制之谓也。易言阴阳。范言五行。而五行出于阴阳。则动静自在其中。
禹贡所谓九山九泽。凡言九者皆出于九畴之数。而弼成五服之制。四方相距各五千里。亦与九畴暗合。
土音为宫。其数八十一。亦九九数也。徵三分减一。为六九五十四。商益其一。而为八九七十二。律吕亦祖于此。
日月之行。则有冬夏。青白朱黑四道。阴阳二历。皆与黄道相会。故曰月行有九道。所谓九道。如九个丝线周而匝之。层层相纠。内层之东。为外层之西。内层之西。为外层之东。而南北与间方。皆照此。西南为朱。东北为黑。东南为青。西北为白。
箕子东之朝鲜。教民八条。所谓八条。即三八政。而东俗贸贸。不得传其详。惟见于汉书。而只传其三条。意者八政其纲领也。三条其条目也。
世传箕子以东俗木强。种柳于平壤。谓之柳京。柳者卉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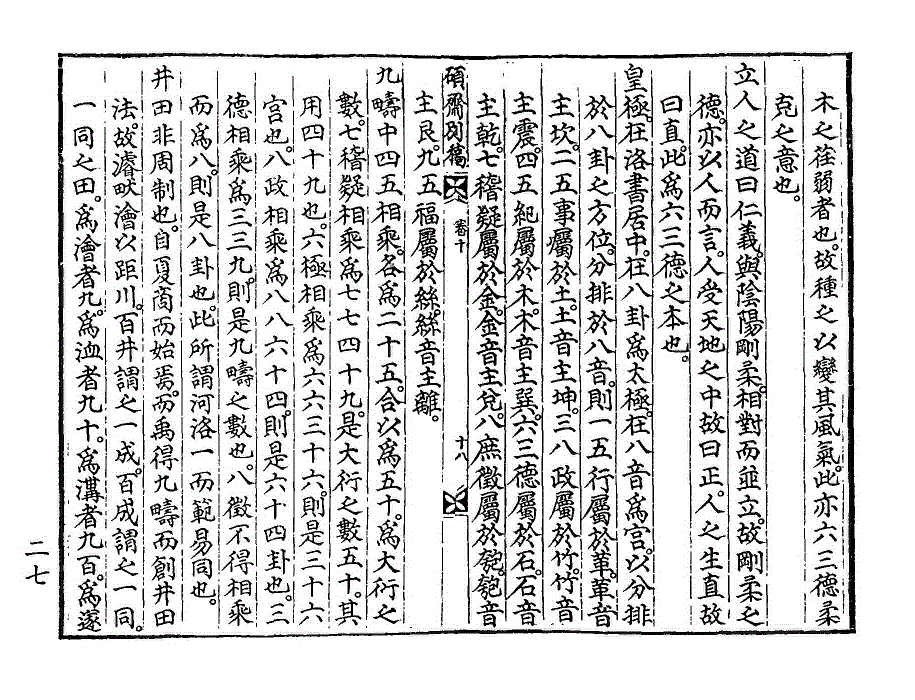 木之荏弱者也。故种之以变其风气。此亦六三德柔克之意也。
木之荏弱者也。故种之以变其风气。此亦六三德柔克之意也。立人之道曰仁义。与阴阳刚柔。相对而并立。故刚柔之德。亦以人而言。人受天地之中故曰正。人之生直故曰直。此为六三德之本也。
皇极。在洛书居中。在八卦为太极。在八音为宫。以分排于八卦之方位。分排于八音。则一五行属于革。革音主坎。二五事属于土。土音主坤。三八政属于竹。竹音主震。四五纪属于木。木音主巽。六三德属于石。石音主乾。七稽疑属于金。金音主兑。八庶徵属于匏。匏音主艮。九五福属于丝。丝音主离。
九畴中四五相乘。各为二十五。合以为五十。为大衍之数。七稽疑相乘为七七四十九。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也。六极相乘为六六三十六。则是三十六宫也。八政相乘为八八六十四。则是六十四卦也。三德相乘为三三九。则是九畴之数也。八徵不得相乘而为八。则是八卦也。此所谓河洛一而范易同也。
井田非周制也。自夏商而始焉。而禹得九畴而创井田法。故浚畎浍以距川。百井谓之一成。百成谓之一同。一同之田。为浍者九。为洫者九十。为沟者九百。为遂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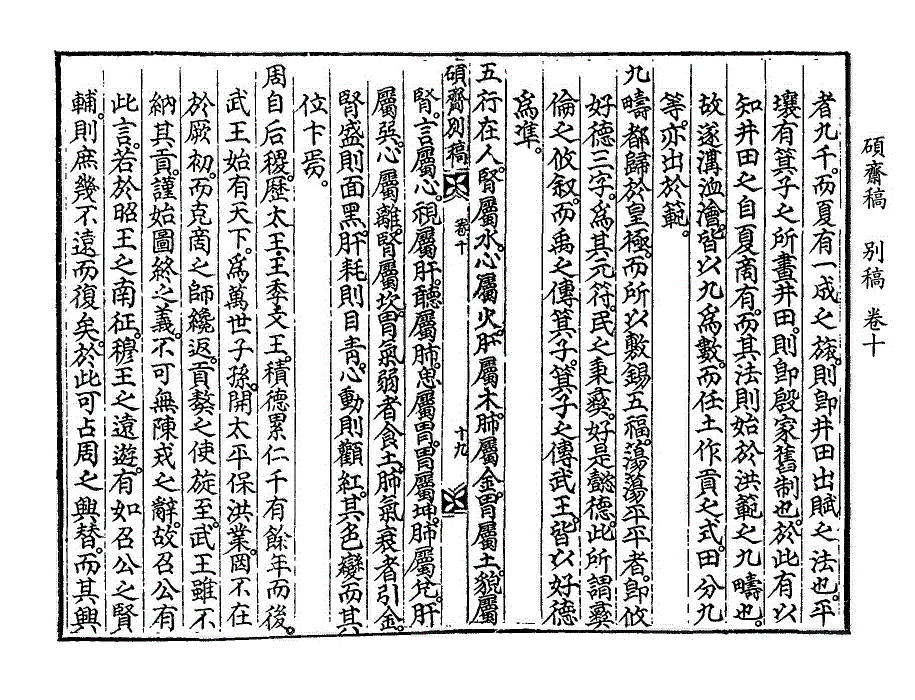 者九千。而夏有一成之旅。则即井田出赋之法也。平壤有箕子之所画井田。则即殷家旧制也。于此有以知井田之自夏商有。而其法则始于洪范之九畴也。故遂沟洫浍。皆以九为数。而任土作贡之式。田分九等。亦出于范。
者九千。而夏有一成之旅。则即井田出赋之法也。平壤有箕子之所画井田。则即殷家旧制也。于此有以知井田之自夏商有。而其法则始于洪范之九畴也。故遂沟洫浍。皆以九为数。而任土作贡之式。田分九等。亦出于范。九畴都归于皇极。而所以敷锡五福。荡荡平平者。即攸好德三字。为其元符。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所谓彝伦之攸叙。而禹之传箕子。箕子之传武王。皆以好德为准。
五行在人。肾属水。心属火。肝属木。肺属金。胃属土。貌属肾。言属心。视属肝。听属肺。思属胃。胃属坤。肺属兑。肝属巽。心属离。肾属坎。胃气弱者食土。肺气衰者引金。肾盛则面黑。肝耗则目青。心动则颧红。其色变而其位卞焉。
周自后稷。历太王,王季,文王。积德累仁千有馀年而后。武王始有天下。为万世子孙。开太平保洪业。罔不在于厥初。而克商之师才返。贡獒之使旋至。武王虽不纳其贡。谨始图终之义。不可无陈戒之辞。故召公有此言。若于昭王之南征。穆王之远游。有如召公之贤辅。则庶几不远而复矣。于此可占周之兴替。而其兴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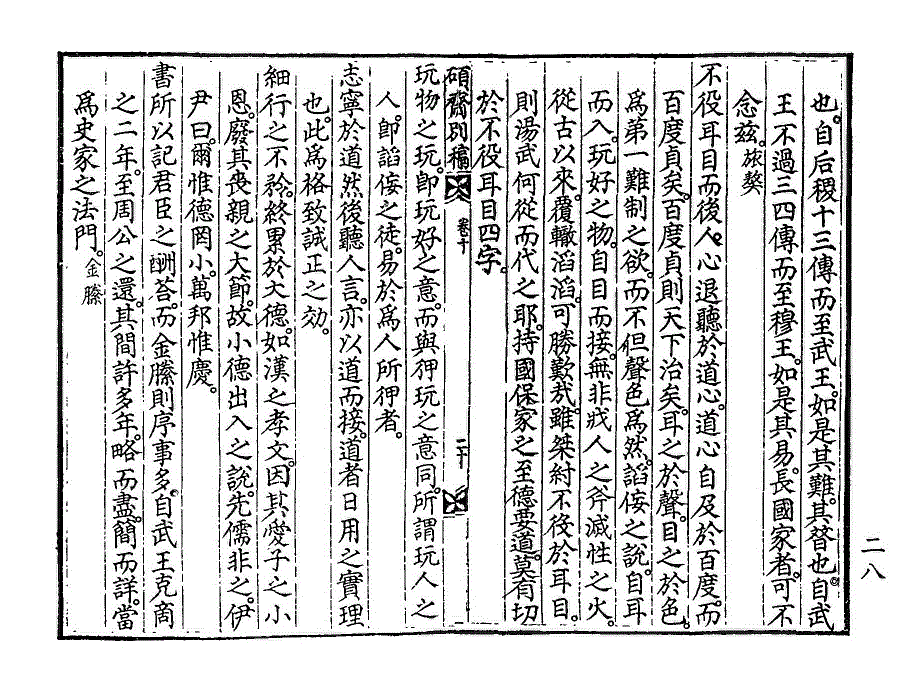 也。自后稷十三传而至武王。如是其难。其替也。自武王不过三四传而至穆王。如是其易。长国家者。可不念玆。(旅獒)
也。自后稷十三传而至武王。如是其难。其替也。自武王不过三四传而至穆王。如是其易。长国家者。可不念玆。(旅獒)不役耳目而后。人心退听于道心。道心自及于百度。而百度贞矣。百度贞则天下治矣。耳之于声。目之于色。为第一难制之欲。而不但声色为然。谄佞之说。自耳而入。玩好之物。自目而接。无非戕人之斧灭性之火。从古以来。覆辙滔滔。可胜叹哉。虽桀纣不役于耳目。则汤武何从而代之耶。持国保家之至德要道。莫有切于不役耳目四字。
玩物之玩。即玩好之意。而与狎玩之意同。所谓玩人之人。即谄佞之徒。易于为人所狎者。
志宁于道然后听人言。亦以道而接。道者日用之实理也。此为格致诚正之效。
细行之不矜。终累于大德。如汉之孝文。因其爱子之小恩。废其丧亲之大节。故小德出入之说。先儒非之。伊尹曰。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
书所以记君臣之酬答。而金縢则序事多。自武王克商之二年。至周公之还。其间许多年。略而尽。简而详。当为史家之法门。(金縢)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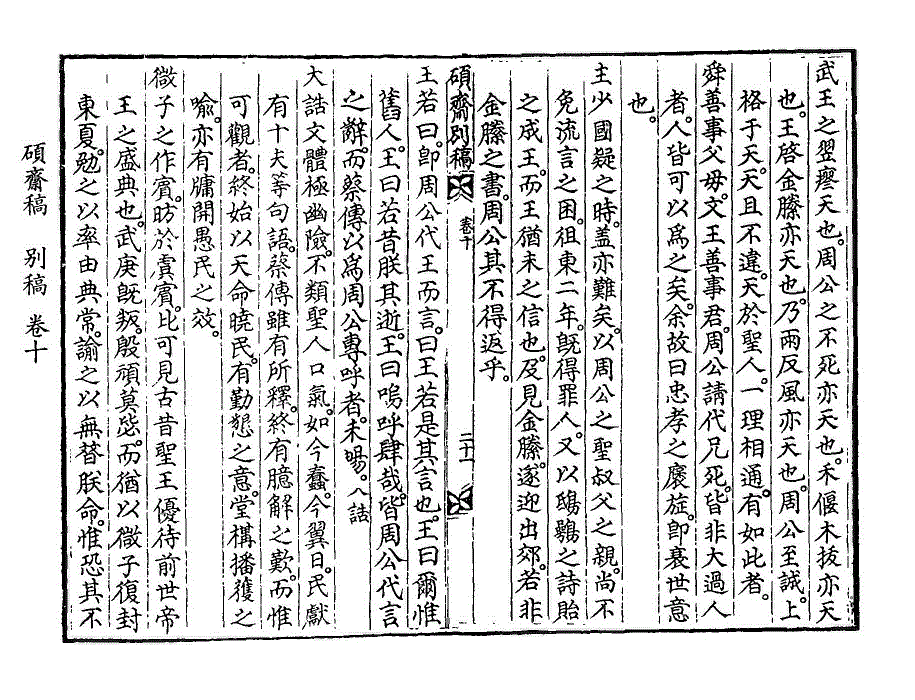 武王之翌瘳天也。周公之不死亦天也。禾偃木拔亦天也。王启金縢亦天也。乃雨反风亦天也。周公至诚。上格于天。天且不违。天于圣人。一理相通。有如此者。
武王之翌瘳天也。周公之不死亦天也。禾偃木拔亦天也。王启金縢亦天也。乃雨反风亦天也。周公至诚。上格于天。天且不违。天于圣人。一理相通。有如此者。舜善事父母。文王善事君。周公请代兄死。皆非大过人者。人皆可以为之矣。余故曰忠孝之褒㫌。即衰世意也。
主少国疑之时。盖亦难矣。以周公之圣叔父之亲。尚不免流言之困。徂东二年。既得罪人。又以鸱鹗之诗贻之成王。而王犹未之信也。及见金縢。遂迎出郊。若非金縢之书。周公其不得返乎。
王若曰。即周公代王而言。曰王若是其言也。王曰尔惟旧人。王曰若昔朕其逝。王曰呜呼肆哉。皆周公代言之辞。而蔡传以为周公专呼者。未畅。(大诰)
大诰文体极幽险。不类圣人口气。如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等句语。蔡传虽有所释。终有臆解之叹。而惟可观者。终始以天命晓民。有勤恳之意。堂构播获之喻。亦有牖开愚民之效。
微子之作宾。昉于虞宾。此可见古昔圣王优待前世帝王之盛典也。武庚既叛。殷顽莫毖。而犹以微子复封东夏。勉之以率由典常。谕之以无替朕命。惟恐其不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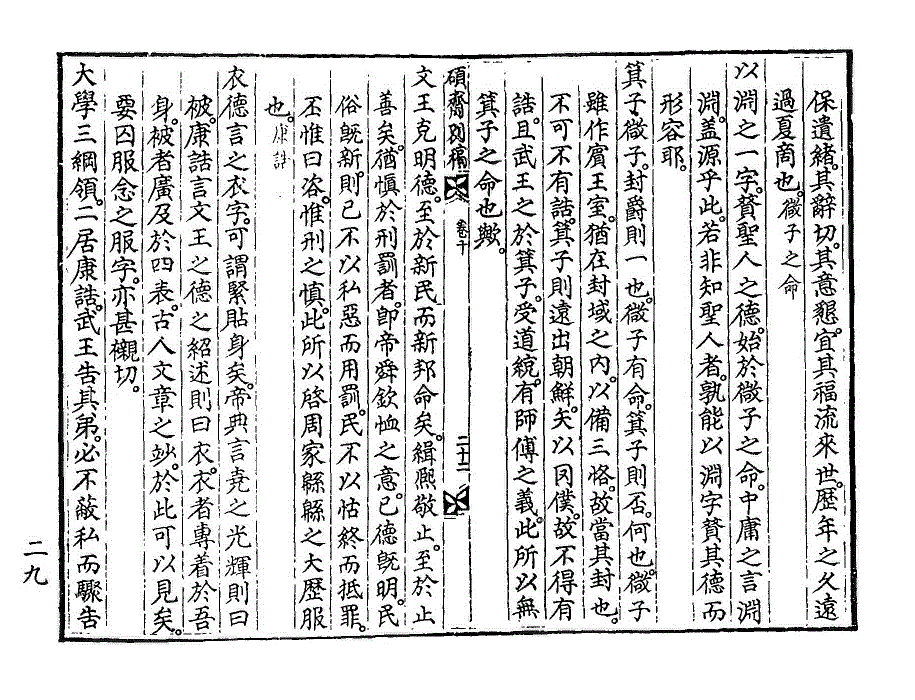 保遗绪。其辞切。其意恳。宜其福流来世。历年之久远过夏商也。(微子之命)
保遗绪。其辞切。其意恳。宜其福流来世。历年之久远过夏商也。(微子之命)以渊之一字。赞圣人之德。始于微子之命。中庸之言渊渊。盖源乎此。若非知圣人者。孰能以渊字赞其德而形容耶。
箕子,微子。封爵则一也。微子有命。箕子则否。何也。微子虽作宾王室。犹在封域之内。以备三恪。故当其封也。不可不有诰。箕子则远出朝鲜。矢以罔仆。故不得有诰。且武王之于箕子。受道统。有师傅之义。此所以无箕子之命也欤。
文王克明德。至于新民而新邦命矣。缉熙敬止。至于止善矣。犹慎于刑罚者。即帝舜钦恤之意。己德既明。民俗既新。则己不以私恶而用罚。民不以怙终而抵罪。丕惟曰咨。惟刑之慎。此所以启周家绵绵之大历服也。(康诰)
衣德言之衣字。可谓紧贴身矣。帝典言尧之光辉则曰被。康诰言文王之德之绍述则曰衣。衣者专着于吾身。被者广及于四表。古人文章之妙。于此可以见矣。要囚服念之服字。亦甚衬切。
大学三纲领。二居康诰。武王告其弟。必不蔽私而骤告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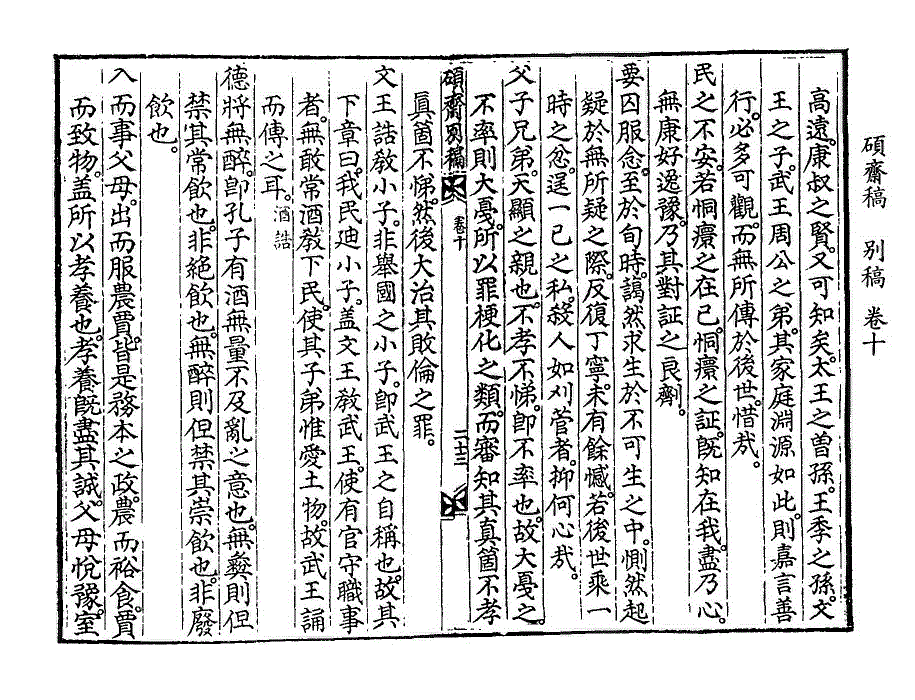 高远。康叔之贤。又可知矣。太王之曾孙。王季之孙。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其家庭渊源如此。则嘉言善行。必多可观。而无所传于后世。惜哉。
高远。康叔之贤。又可知矣。太王之曾孙。王季之孙。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其家庭渊源如此。则嘉言善行。必多可观。而无所传于后世。惜哉。民之不安。若恫瘝之在己。恫瘝之证。既知在我。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对证之良剂。
要囚服念。至于旬时。蔼然求生于不可生之中。恻然起疑于无所疑之际。反复丁宁。未有馀憾。若后世乘一时之忿。逞一己之私。杀人如刈菅者。抑何心哉。
父子兄弟。天显之亲也。不孝不悌。即不率也。故大戛之。不率则大戛。所以罪梗化之类。而审知其真个不孝真个不悌。然后大治其败伦之罪。
文王诰教小子。非举国之小子。即武王之自称也。故其下章曰。我民迪小子。盖文王教武王。使有官守职事者。无敢常酒。教下民。使其子弟惟爱土物。故武王诵而传之耳。(酒诰)
德将无醉。即孔子有酒无量不及乱之意也。无彝则但禁其常饮也。非绝饮也。无醉则但禁其崇饮也。非废饮也。
入而事父母。出而服农贾。皆是务本之政。农而裕食。贾而致物。盖所以孝养也。孝养既尽其诚。父母悦豫。室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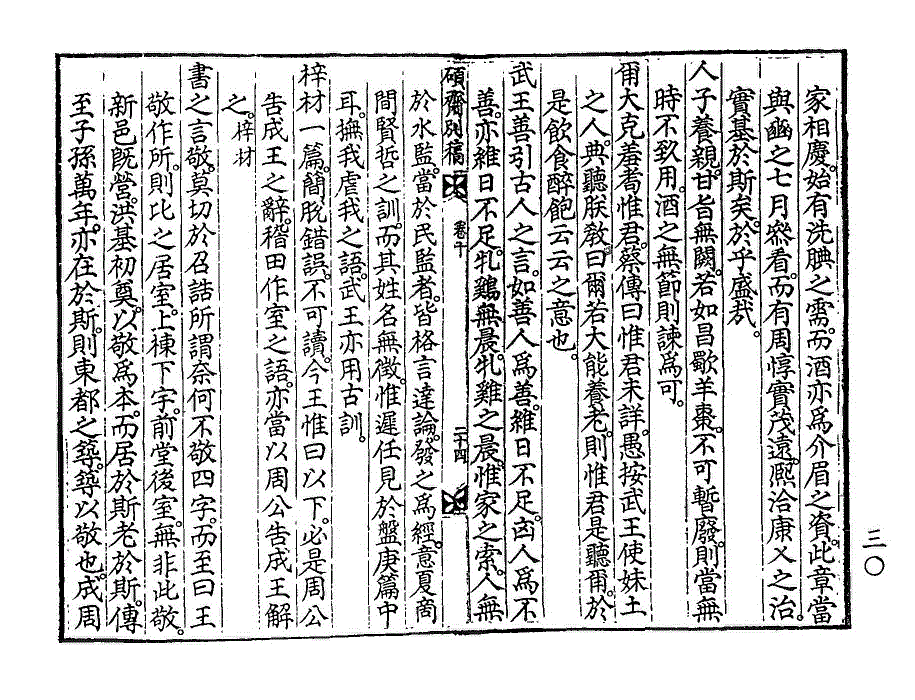 家相庆。始有洗腆之需。而酒亦为介眉之资。此章当与豳之七月参看。而有周惇实茂远。熙洽康乂之治。实基于斯矣。于乎盛哉。
家相庆。始有洗腆之需。而酒亦为介眉之资。此章当与豳之七月参看。而有周惇实茂远。熙洽康乂之治。实基于斯矣。于乎盛哉。人子养亲。甘旨无阙。若如昌歜羊枣。不可暂废。则当无时不致用。酒之无节则谏为可。
尔大克羞耇惟君。蔡传曰惟君未详。愚按武王使妹土之人。典听朕教。曰尔若大能养老。则惟君是听尔。于是饮食醉饱云云之意也。
武王善引古人之言。如善人为善。维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维日不足。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者。皆格言达论。发之为经。意夏商间贤哲之训。而其姓名无徵。惟迟任见于盘庚篇中耳。抚我虐我之语。武王亦用古训。
梓材一篇。简脱错误。不可读。今王惟曰以下。必是周公告成王之辞。稽田作室之语。亦当以周公告成王解之。(梓材)
书之言敬。莫切于召诰所谓奈何不敬四字。而至曰王敬作所。则比之居室。上栋下宇。前堂后室。无非此敬。新邑既营。洪基初奠。以敬为本。而居于斯老于斯。传至子孙万年。亦在于斯。则东都之筑。筑以敬也。成周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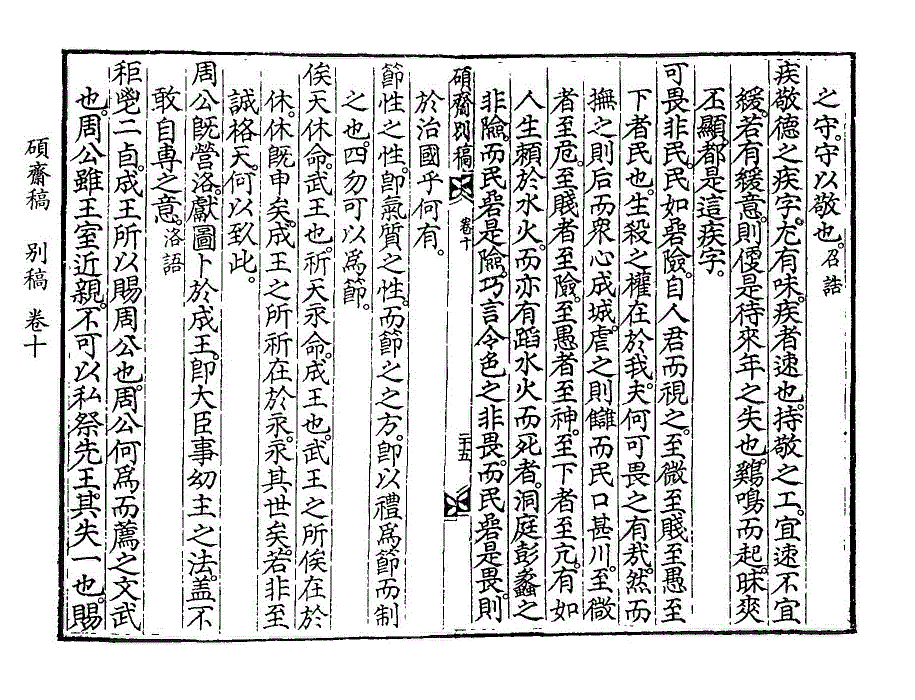 之守。守以敬也。(召诰)
之守。守以敬也。(召诰)疾敬德之疾字。尤有味。疾者速也。持敬之工。宜速不宜缓。若有缓意。则便是待来年之失也。鸡鸣而起。昧爽丕显。都是这疾字。
可畏非民。民如碞险。自人君而视之。至微至贱至愚至下者民也。生杀之权在于我。夫何可畏之有哉。然而抚之则后而众心成城。虐之则雠而民口甚川。至微者至危。至贱者至险。至愚者至神。至下者至亢。有如人生赖于水火。而亦有蹈水火而死者。洞庭彭蠡之非险。而民碞是险。巧言令色之非畏。而民碞是畏。则于治国乎何有。
节性之性。即气质之性。而节之之方。即以礼为节而制之也。四勿可以为节。
俟天休命。武王也。祈天永命。成王也。武王之所俟在于休。休既申矣。成王之所祈在于永。永其世矣。若非至诚格天。何以致此。
周公既营洛。献图卜于成王。即大臣事幼主之法。盖不敢自专之意。(洛语)
秬鬯二卣。成王所以赐周公也。周公何为而荐之文武也。周公虽王室近亲。不可以私祭先王。其失一也。赐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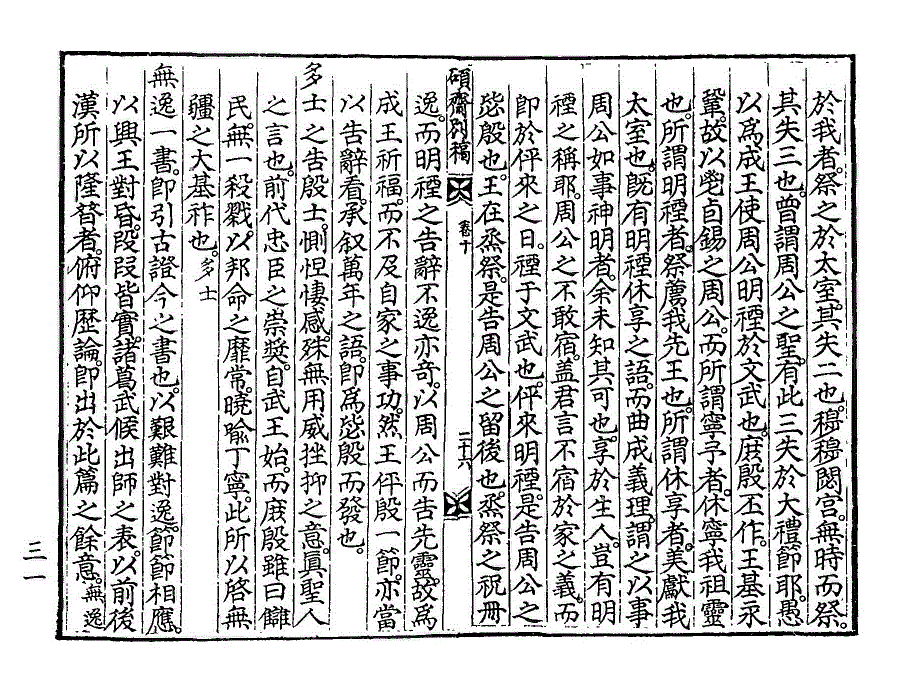 于我者。祭之于太室。其失二也。穆穆閟宫。无时而祭。其失三也。曾谓周公之圣。有此三失于大礼节耶。愚以为成王使周公明禋于文武也。庶殷丕作。王基永巩。故以鬯卣锡之周公。而所谓宁予者。休宁我祖灵也。所谓明禋者。祭荐我先王也。所谓休享者。美献我太室也。既有明禋休享之语。而曲成义理。谓之以事周公如事神明者。余未知其可也。享于生人。岂有明禋之称耶。周公之不敢宿。盖君言不宿于家之义。而即于伻来之日。禋于文武也。伻来明禋。是告周公之毖殷也。王在烝祭。是告周公之留后也。烝祭之祝册逸。而明禋之告辞不逸亦奇。以周公而告先灵。故为成王祈福。而不及自家之事功。然王伻殷一节。亦当以告辞看。承叙万年之语。即为毖殷而发也。
于我者。祭之于太室。其失二也。穆穆閟宫。无时而祭。其失三也。曾谓周公之圣。有此三失于大礼节耶。愚以为成王使周公明禋于文武也。庶殷丕作。王基永巩。故以鬯卣锡之周公。而所谓宁予者。休宁我祖灵也。所谓明禋者。祭荐我先王也。所谓休享者。美献我太室也。既有明禋休享之语。而曲成义理。谓之以事周公如事神明者。余未知其可也。享于生人。岂有明禋之称耶。周公之不敢宿。盖君言不宿于家之义。而即于伻来之日。禋于文武也。伻来明禋。是告周公之毖殷也。王在烝祭。是告周公之留后也。烝祭之祝册逸。而明禋之告辞不逸亦奇。以周公而告先灵。故为成王祈福。而不及自家之事功。然王伻殷一节。亦当以告辞看。承叙万年之语。即为毖殷而发也。多士之告殷士。恻怛悽感。殊无用威挫抑之意。真圣人之言也。前代忠臣之崇奖。自武王始。而庶殷虽曰雠民。无一杀戮。以邦命之靡常。晓喻丁宁。此所以启无疆之大基祚也。(多士)
无逸一书。即引古證今之书也。以艰难对逸。节节相应。以兴王对昏。段段皆实。诸葛武侯出师之表。以前后汉所以隆替者。俯仰历论。即出于此篇之馀意。(无逸)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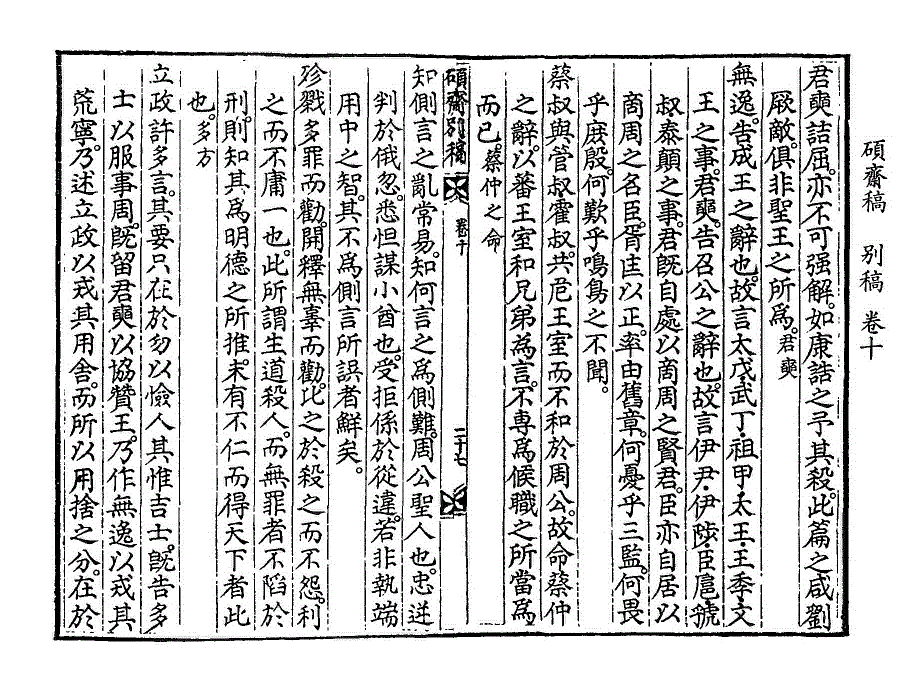 君奭诘屈。亦不可强解。如康诰之予其杀。此篇之咸刘厥敌。俱非圣王之所为。(君奭)
君奭诘屈。亦不可强解。如康诰之予其杀。此篇之咸刘厥敌。俱非圣王之所为。(君奭)无逸。告成王之辞也。故言太戊,武丁,祖甲,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君奭。告召公之辞也。故言伊尹,伊陟,臣扈,虢叔,泰颠之事。君既自处以商周之贤君。臣亦自居以商周之名臣。胥匡以正。率由旧章。何忧乎三监。何畏乎庶殷。何叹乎鸣鸟之不闻。
蔡叔与管叔,霍叔。共危王室而不和于周公。故命蔡仲之辞。以蕃王室和兄弟为言。不专为候职之所当为而已。(蔡仲之命)
知侧言之乱常易。知何言之为侧难。周公圣人也。忠逆判于俄忽。悉怛谋小酋也。受拒系于从违。若非执端用中之智。其不为侧言所误者鲜矣。
殄戮多罪而劝。开释无辜而劝。比之于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一也。此所谓生道杀人。而无罪者不陷于刑。则知其为明德之所推。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此也。(多方)
立政许多言。其要只在于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既告多士以服事周。既留君奭以协赞王。乃作无逸以戒其荒宁。乃述立政以戒其用舍。而所以用舍之分。在于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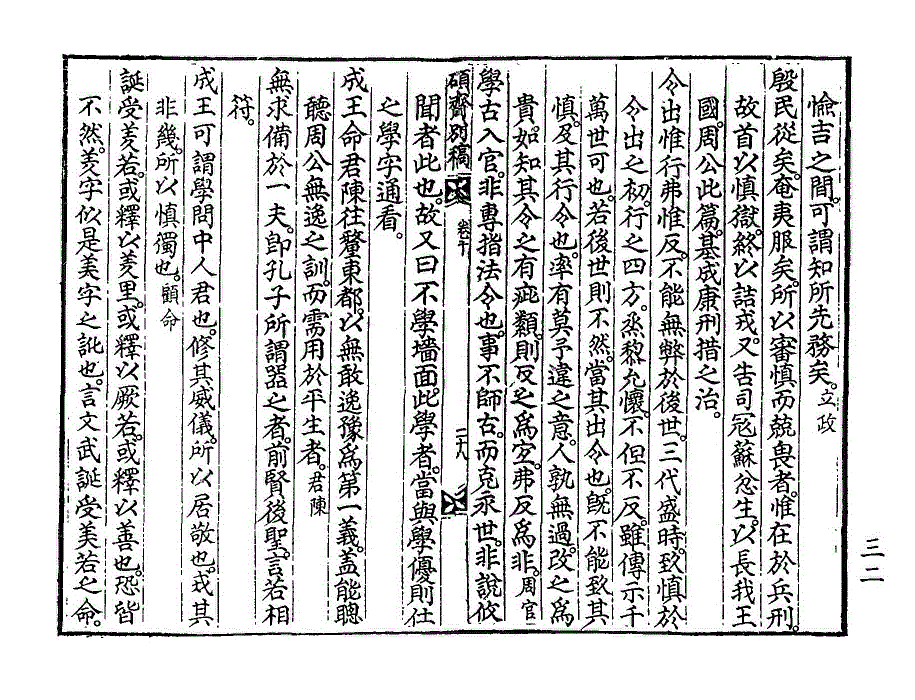 憸吉之间。可谓知所先务矣。(立政)
憸吉之间。可谓知所先务矣。(立政)殷民从矣。奄夷服矣。所以审慎而兢畏者。惟在于兵刑。故首以慎狱。终以诘戎。又告司寇苏忿生。以长我王国。周公此篇。基成康刑措之治。
令出惟行弗惟反。不能无弊于后世。三代盛时。致慎于令出之初。行之四方。烝黎允怀。不但不反。虽传示千万世可也。若后世则不然。当其出令也。既不能致其慎。及其行令也。率有莫予违之意。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如知其令之有疵颣。则反之为宜。弗反为非。(周官)
学古入官。非专指法令也。事不师古。而克永世。非说攸闻者此也。故又曰不学墙面。此学者。当与学优则仕之学字通看。
成王命君陈往釐东都。以无敢逸豫为第一义。盖能聪听周公无逸之训。而需用于平生者。(君陈)
无求备于一夫。即孔子所谓器之者。前贤后圣。言若相符。
成王可谓学问中人君也。修其威仪。所以居敬也。戒其非几。所以慎独也。(顾命)
诞受羑若。或释以羑里。或释以厥若。或释以善也。恐皆不然。羑字似是美字之讹也。言文武诞受美若之命。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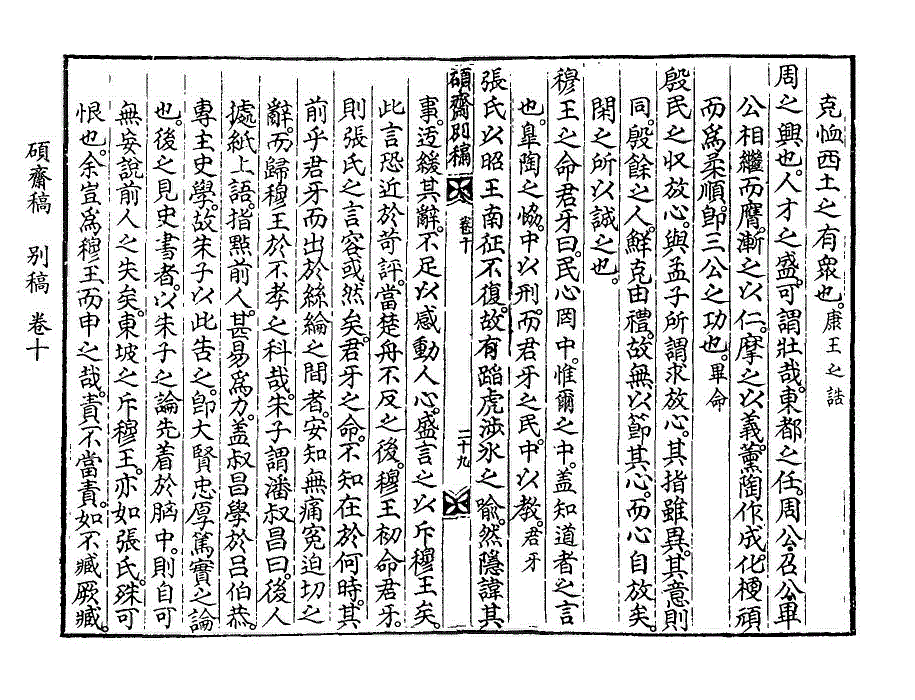 克恤西土之有众也。(康王之诰)
克恤西土之有众也。(康王之诰)周之兴也。人才之盛。可谓壮哉。东都之任。周公,召公,毕公相继而膺。渐之以仁。摩之以义。薰陶作成。化梗顽而为柔顺。即三公之功也。(毕命)
殷民之收放心。与孟子所谓求放心。其指虽异。其意则同。殷馀之人。鲜克由礼。故无以节其心。而心自放矣。闲之所以诚之也。
穆王之命君牙曰。民心罔中。惟尔之中。盖知道者之言也。皋陶之协。中以刑。而君牙之民。中以教。(君牙)
张氏以昭王南征不复。故有蹈虎涉冰之喻。然隐讳其事。迂缓其辞。不足以感动人心。盛言之以斥穆王矣。此言恐近于苛评。当楚舟不反之后。穆王初命君牙。则张氏之言容或然矣。君牙之命。不知在于何时。其前乎君牙而出于丝纶之间者。安知无痛冤迫切之辞。而归穆王于不孝之科哉。朱子谓潘叔昌曰。后人据纸上语。指点前人。甚易为力。盖叔昌学于吕伯恭。专主史学。故朱子以此告之。即大贤忠厚笃实之论也。后之见史书者。以朱子之论先着于胸中。则自可无妄说前人之失矣。东坡之斥穆王。亦如张氏。殊可恨也。余岂为穆王而申之哉。责不当责。如不臧厥臧。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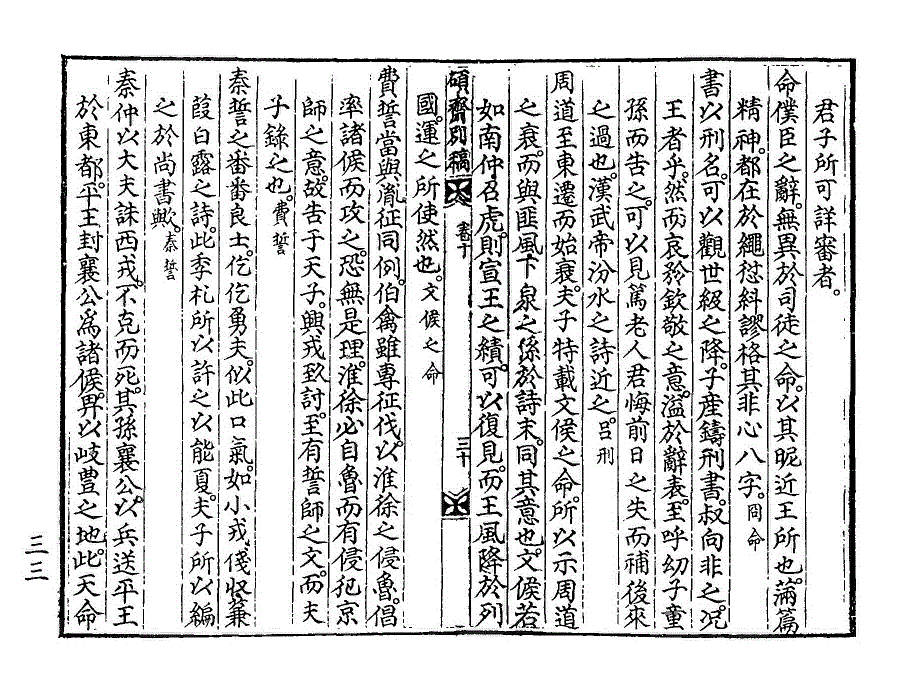 君子所可详审者。
君子所可详审者。命仆臣之辞。无异于司徒之命。以其昵近王所也。满篇精神。都在于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八字。(囧命)
书以刑名。可以观世级之降。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况王者乎。然而哀矜钦敬之意。溢于辞表。至呼幼子童孙而告之。可以见笃老人君悔前日之失而补后来之过也。汉武帝汾水之诗近之。(吕刑)
周道至东迁而始衰。夫子特载文侯之命。所以示周道之衰。而与匪风,下泉之系于诗末。同其意也。文侯若如南仲,召虎。则宣王之绩。可以复见。而王风降于列国。运之所使然也。(文侯之命)
费誓当与胤征同例。伯禽虽专征伐。以淮徐之侵鲁。倡率诸侯而攻之。恐无是理。淮徐必自鲁而有侵犯京师之意。故告于天子。兴戎致讨。至有誓师之文。而夫子录之也。(费誓)
秦誓之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似此口气。如小戎俴收,蒹葭白露之诗。此季札所以许之以能夏。夫子所以编之于尚书欤。(秦誓)
秦仲以大夫诛西戎。不克而死。其孙襄公。以兵送平王于东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畀以岐礼之地。此天命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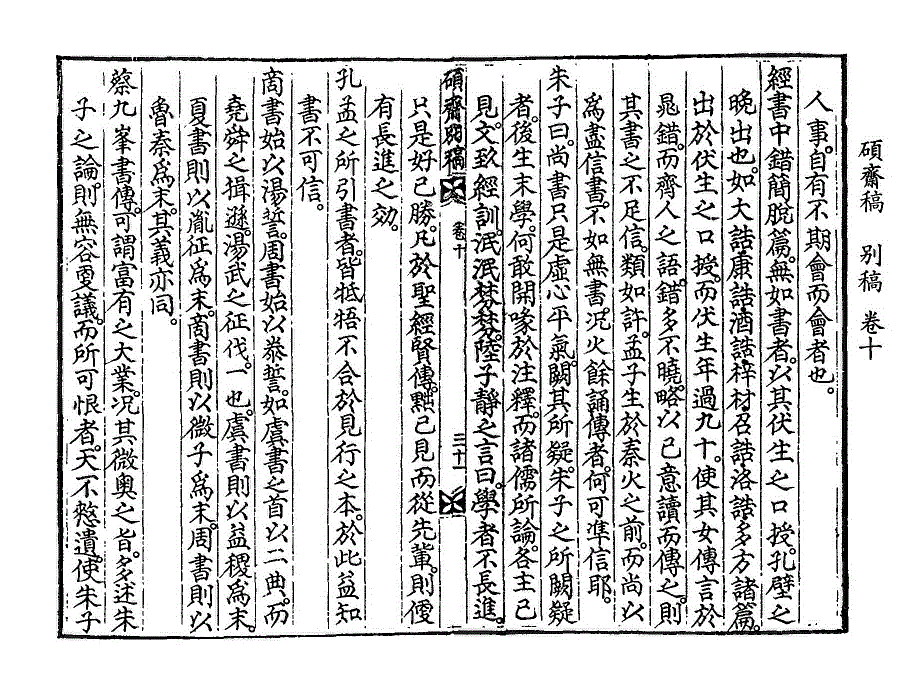 人事。自有不期会而会者也。
人事。自有不期会而会者也。经书中错简脱篇。无如书者。以其伏生之口授。孔壁之晚出也。如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诸篇。出于伏生之口授。而伏生年过九十。使其女传言于晁错。而齐人之语。错多不晓。略以己意读而传之。则其书之不足信。类如许。孟子生于秦火之前。而尚以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况火馀诵传者。何可准信耶。
朱子曰。尚书只是虚心平气。阙其所疑。朱子之所阙疑者。后生末学。何敢开喙于注释。而诸儒所论。各主己见。文致经训。泯泯棼棼。陆子静之言曰。学者不长进。只是好己胜。凡于圣经贤传。黜己见而从先辈。则便有长进之效。
孔孟之所引书者。皆牴牾不合于见行之本。于此益知书不可信。
商书始以汤誓。周书始以泰誓。如虞书之首以二典。而尧舜之揖逊。汤武之征伐。一也。虞书则以益稷为末。夏书则以胤征为末。商书则以微子为末。周书则以鲁秦为末。其义亦同。
蔡九峰书传。可谓富有之大业。况其微奥之旨。多述朱子之论。则无容更议。而所可恨者。天不慭遗。使朱子
硕斋别稿卷之十 第 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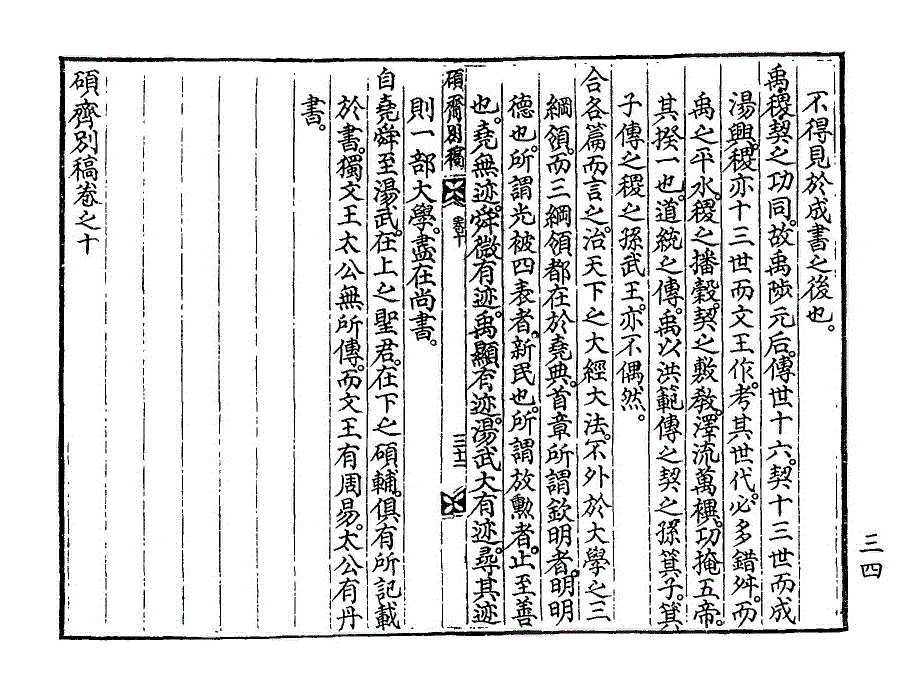 不得见于成书之后也。
不得见于成书之后也。禹,稷,契之功同。故禹陟元后。传世十六。契十三世而成汤兴。稷亦十三世而文王作。考其世代。必多错舛。而禹之平水。稷之播谷。契之敷教。泽流万祀。功掩五帝。其揆一也。道统之传。禹以洪范传之契之孙箕子。箕子传之稷之孙武王。亦不偶然。
合各篇而言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不外于大学之三纲领。而三纲领都在于尧典。首章所谓钦明者。明明德也。所谓光被四表者。新民也。所谓放勋者。止至善也。尧无迹。舜微有迹。禹显有迹。汤武大有迹。寻其迹则一部大学。尽在尚书。
自尧舜至汤武。在上之圣君。在下之硕辅。俱有所记载于书。独文王太公无所传。而文王有周易。太公有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