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九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余于易。虽有所记。其微妙之旨。顾茫然不识其津筏。第取尚书继之。而土室老炎。无以极意细绎。可恨亦可笑也。昔我伯氏守默堂先生。幼时受尚书于皇考。读禹贡三遍。辄成诵。不错一字。如小子不肖。无能为役于父兄。而荒坠家训。身陷大戾。瞻望祠宇。汗泪交迸。对此方策。秪增抑塞。而强意漫题如此云尔。
尚书[上]
尧之被四之光由于明。明由于文。文由于思。思由于钦。七十载无为之治。蔽一钦字。(尧典)
先儒王与耕以安安允克。尧异于人为说。此与孟子与人同之训不同。尧性之者也。故不勉而行。尧之性与人之性。同一性也。性之则人皆可以为尧。尧岂异诸人哉。若云异于人乎。则人必退缩而不以尧自期。岂细忧哉。
亲九族。所以亲亲也。协万邦。所以仁民也。亲亲仁民。皆由于明明德。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余于易。虽有所记。其微妙之旨。顾茫然不识其津筏。第取尚书继之。而土室老炎。无以极意细绎。可恨亦可笑也。昔我伯氏守默堂先生。幼时受尚书于皇考。读禹贡三遍。辄成诵。不错一字。如小子不肖。无能为役于父兄。而荒坠家训。身陷大戾。瞻望祠宇。汗泪交迸。对此方策。秪增抑塞。而强意漫题如此云尔。
尚书[上]
尧之被四之光由于明。明由于文。文由于思。思由于钦。七十载无为之治。蔽一钦字。(尧典)
先儒王与耕以安安允克。尧异于人为说。此与孟子与人同之训不同。尧性之者也。故不勉而行。尧之性与人之性。同一性也。性之则人皆可以为尧。尧岂异诸人哉。若云异于人乎。则人必退缩而不以尧自期。岂细忧哉。
亲九族。所以亲亲也。协万邦。所以仁民也。亲亲仁民。皆由于明明德。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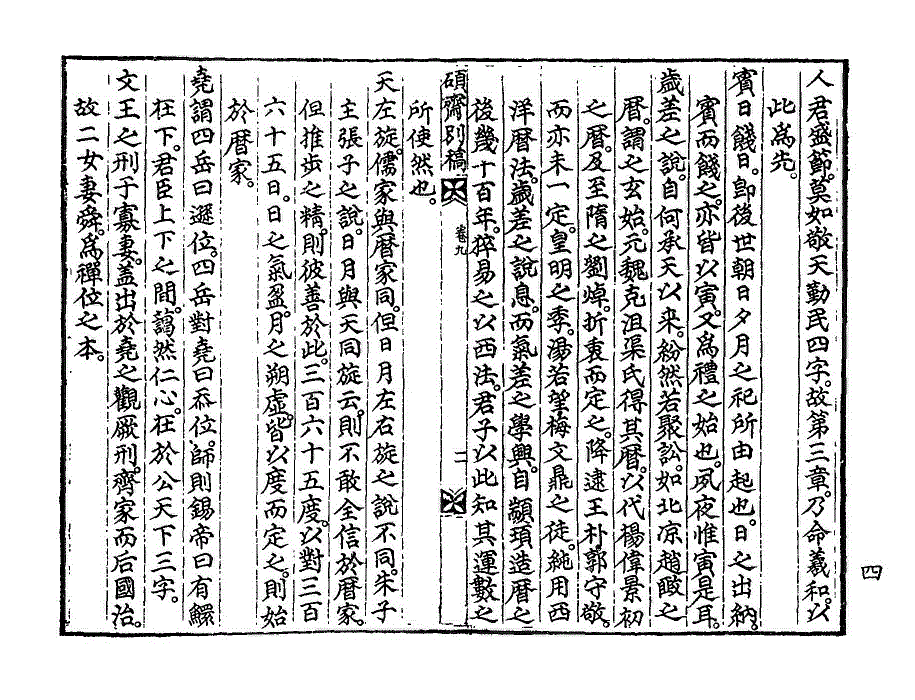 人君盛节。莫如敬天勤民四字。故第三章。乃命羲和。以此为先。
人君盛节。莫如敬天勤民四字。故第三章。乃命羲和。以此为先。宾日饯日。即后世朝日夕月之祀所由起也。日之出纳。宾而饯之。亦皆以寅。又为礼之始也。夙夜惟寅是耳。
岁差之说。自何承天以来。纷然若聚讼。如北凉赵𢾺之历。谓之玄始。元魏克沮渠氏得其历。以代杨伟景初之历。及至隋之刘焯。折衷而定之。降逮王朴,郭守敬。而亦未一定。皇明之季。汤若望,梅文鼎之徒。纯用西洋历法。岁差之说息。而气差之学兴。自颛顼造历之后几十百年。猝易之以西法。君子以此知其运数之所使然也。
天左旋。儒家与历家同。但日月左右旋之说不同。朱子主张子之说。日月与天同旋云。则不敢全信于历家。但推步之精。则彼善于此。三百六十五度。以对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气盈。月之朔虚。皆以度而定之。则始于历家。
尧谓四岳曰逊位。四岳对尧曰忝位。师则锡帝曰有鳏在下。君臣上下之间。蔼然仁心。在于公天下三字。
文王之刑于寡妻。盖出于尧之观厥刑。齐家而后国治。故二女妻舜。为禅位之本。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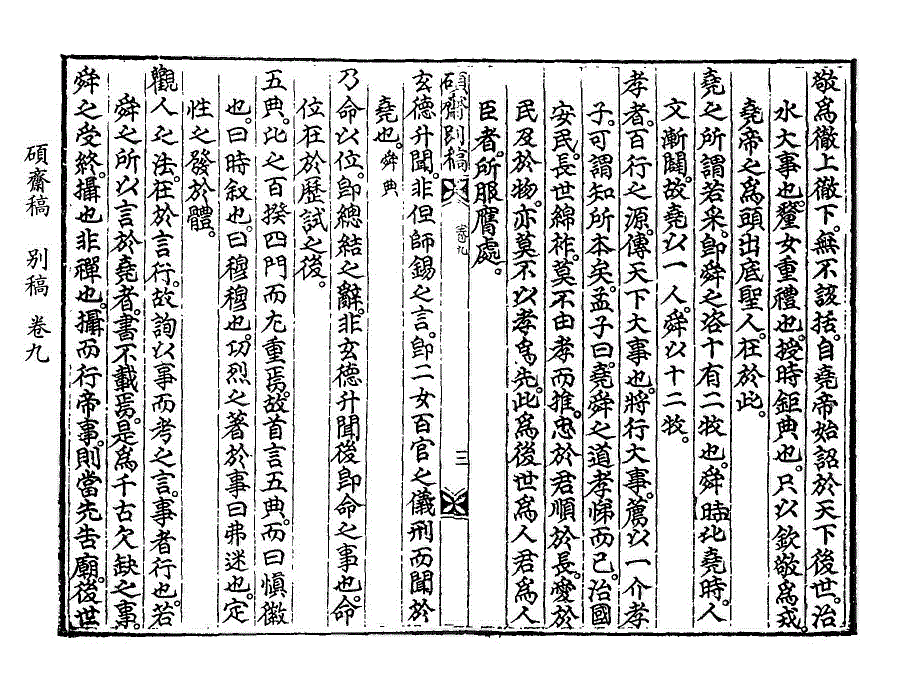 敬为彻上彻下。无不该括。自尧帝始诏于天下后世。治水大事也。釐女重礼也。授时钜典也。只以钦敬为戒。尧帝之为头出底圣人。在于此。
敬为彻上彻下。无不该括。自尧帝始诏于天下后世。治水大事也。釐女重礼也。授时钜典也。只以钦敬为戒。尧帝之为头出底圣人。在于此。尧之所谓若采。即舜之咨十有二牧也。舜时比尧时。人文渐辟。故尧以一人。舜以十二牧。
孝者。百行之源。传天下大事也。将行大事。荐以一介孝子。可谓知所本矣。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治国安民。长世绵祚。莫不由孝而推。忠于君顺于长。爱于民及于物。亦莫不以孝为先。此为后世为人君为人臣者。所服膺处。
玄德升闻。非但师锡之言。即二女百官之仪刑而闻于尧也。(舜典)
乃命以位。即总结之辞。非玄德升闻后即命之事也。命位在于历试之后。
五典。比之百揆四门而尤重焉。故首言五典。而曰慎徽也。曰时叙也。曰穆穆也。功烈之著于事曰弗迷也。定性之发于体。
观人之法。在于言行。故询以事而考之言。事者行也。若舜之所以言于尧者。书不载焉。是为千古欠缺之事。
舜之受终。摄也非禅也。摄而行帝事。则当先告庙。后世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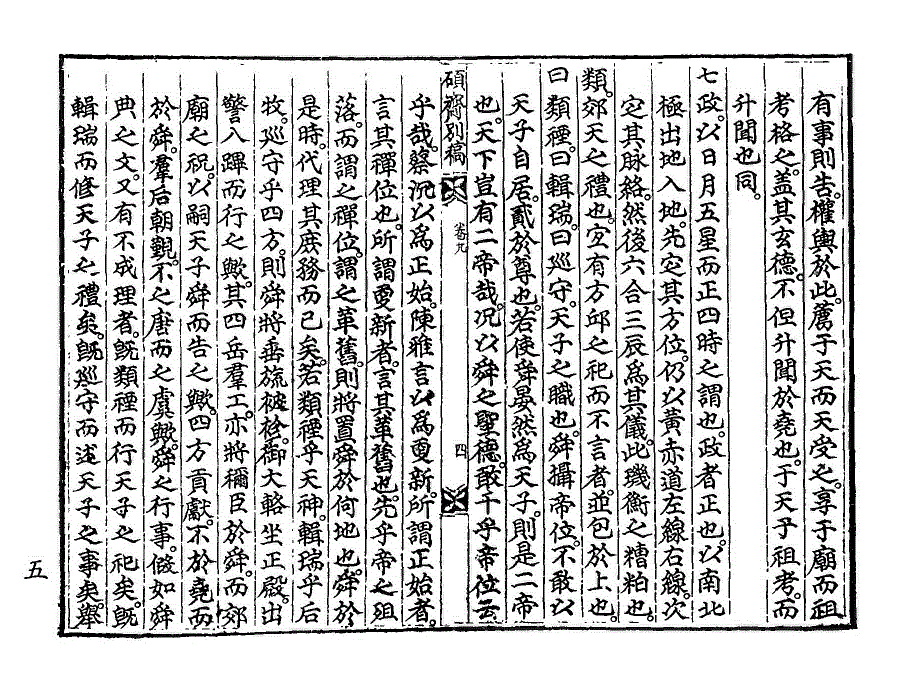 有事则告。权舆于此。荐于天而天受之。享于庙而祖考格之。盖其玄德。不但升闻于尧也。于天于祖考。而升闻也同。
有事则告。权舆于此。荐于天而天受之。享于庙而祖考格之。盖其玄德。不但升闻于尧也。于天于祖考。而升闻也同。七政。以日月五星而正四时之谓也。政者正也。以南北极出地入地。先定其方位。仍以黄赤道左线右线。次定其脉络。然后六合三辰为其仪。此玑衡之糟粕也。
类。郊天之礼也。宜有方邱之祀而不言者。并包于上也。
曰类禋。曰辑瑞。曰巡守。天子之职也。舜摄帝位。不敢以天子自居。贰于尊也。若使舜晏然为天子。则是二帝也。天下岂有二帝哉。况以舜之圣德。敢干乎帝位云乎哉。蔡沉以为正始。陈雅言以为更新。所谓正始者。言其禅位也。所谓更新者。言其革旧也。先乎帝之殂落。而谓之禅位。谓之革旧。则将置舜于何地也。舜于是时。代理其庶务而已矣。若类禋乎天神。辑瑞乎后牧。巡守乎四方。则舜将垂旒被袗。御大辂坐正殿。出警入跸而行之欤。其四岳群工。亦将称臣于舜。而郊庙之祝。以嗣天子舜而告之欤。四方贡献。不于尧而于舜。群后朝觐。不之唐而之虞欤。舜之行事。假如舜典之文。又有不成理者。既类禋而行天子之祀矣。既辑瑞而修天子之礼矣。既巡守而述天子之事矣。举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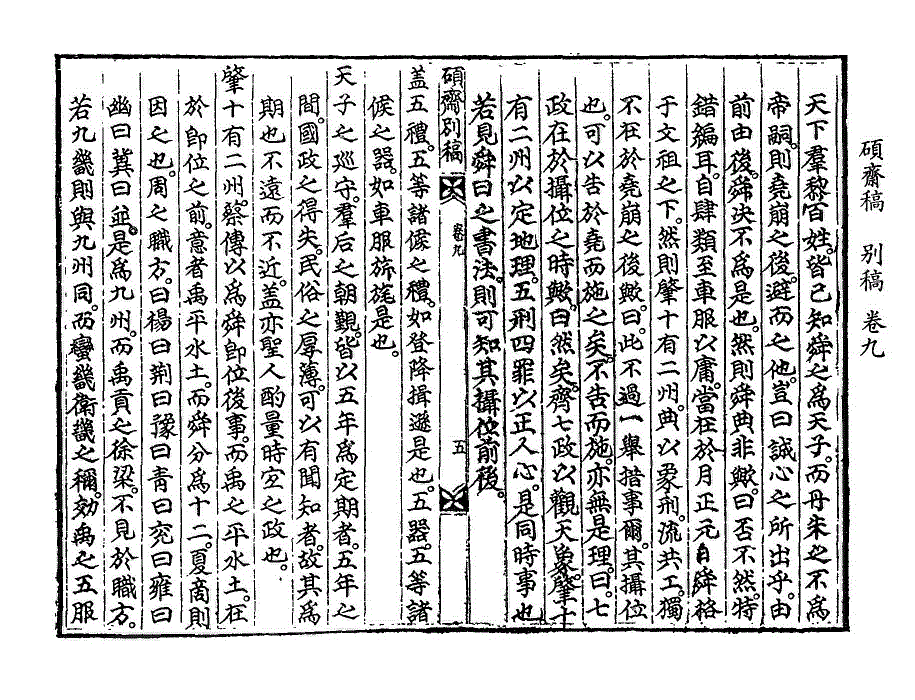 天下群黎百姓。皆已知舜之为天子。而丹朱之不为帝嗣。则尧崩之后。避而之他。岂曰诚心之所出乎。由前由后。舜决不为是也。然则舜典非欤。曰否不然。特错编耳。自肆类至车服以庸。当在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下。然则肇十有二州。典以象刑。流共工。独不在于尧崩之后欤。曰。此不过一举措事尔。其摄位也。可以告于尧而施之矣。不告而施。亦无是理。曰。七政在于摄位之时欤。曰然矣。齐七政以观天象。肇十有二州以定地理。五刑四罪以正人心。是同时事也。若见舜曰之书法。则可知其摄位前后。
天下群黎百姓。皆已知舜之为天子。而丹朱之不为帝嗣。则尧崩之后。避而之他。岂曰诚心之所出乎。由前由后。舜决不为是也。然则舜典非欤。曰否不然。特错编耳。自肆类至车服以庸。当在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下。然则肇十有二州。典以象刑。流共工。独不在于尧崩之后欤。曰。此不过一举措事尔。其摄位也。可以告于尧而施之矣。不告而施。亦无是理。曰。七政在于摄位之时欤。曰然矣。齐七政以观天象。肇十有二州以定地理。五刑四罪以正人心。是同时事也。若见舜曰之书法。则可知其摄位前后。盖五礼。五等诸侯之礼。如登降揖逊是也。五器。五等诸侯之器。如车服旂旄是也。
天子之巡守。群后之朝觐。皆以五年为定期者。五年之间。国政之得失。民俗之厚薄。可以有闻知者。故其为期也不远而不近。盖亦圣人酌量时宜之政也。
肇十有二州。蔡传以为舜即位后事。而禹之平水土。在于即位之前。意者禹平水土。而舜分为十二。夏商则因之也。周之职方。曰杨曰荆曰豫曰青曰兖曰雍曰幽曰冀曰并。是为九州。而禹贡之徐梁。不见于职方。若九畿则与九州同。而蛮畿卫畿之称。效禹之五服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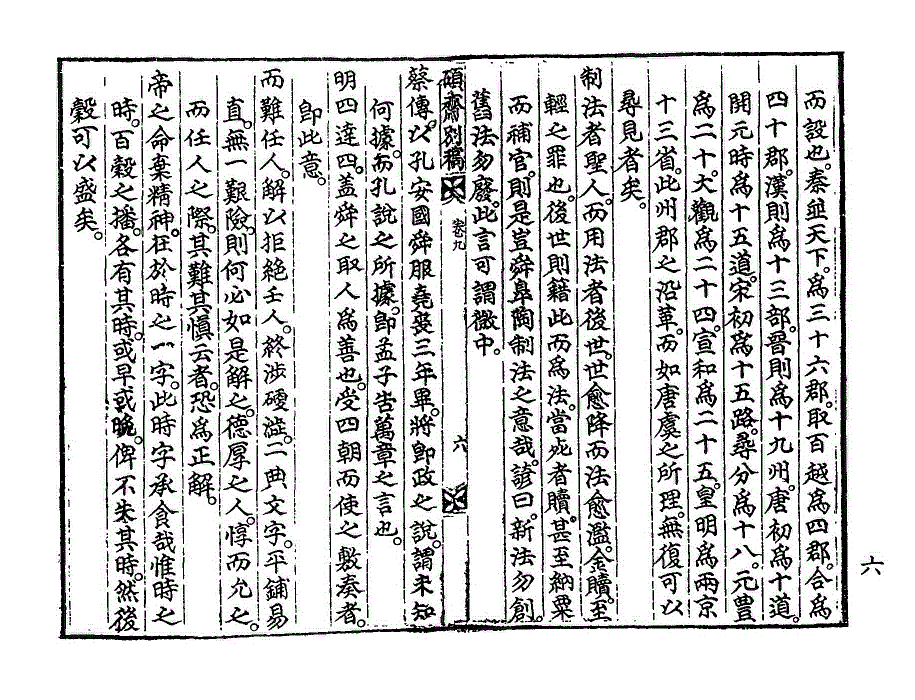 而设也。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取百越为四郡。合为四十郡。汉则为十三部。晋则为十九州。唐初为十道。开元时为十五道。宋初为十五路。寻分为十八。元礼为二十。大观为二十四。宣和为二十五。皇明为两京十三省。此州郡之沿革。而如唐虞之所理。无复可以寻见者矣。
而设也。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取百越为四郡。合为四十郡。汉则为十三部。晋则为十九州。唐初为十道。开元时为十五道。宋初为十五路。寻分为十八。元礼为二十。大观为二十四。宣和为二十五。皇明为两京十三省。此州郡之沿革。而如唐虞之所理。无复可以寻见者矣。制法者圣人。而用法者后世。世愈降而法愈滥。金赎。至轻之罪也。后世则籍此而为法。当死者赎。甚至纳粟而补官。则是岂舜皋陶制法之意哉。谚曰。新法勿创。旧法勿废。此言可谓微中。
蔡传。以孔安国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之说。谓未知何据。而孔说之所据。即孟子告万章之言也。
明四达四。盖舜之取人为善也。受四朝而使之敷奏者。即此意。
而难任人。解以拒绝壬人。终涉硬涩。二典文字。平铺易直。无一艰险。则何必如是解之。德厚之人。惇而允之。而任人之际。其难其慎云者。恐为正解。
帝之命弃精神。在于时之一字。此时字承食哉惟时之时。百谷之播。各有其时。或早或晚。俾不失其时。然后谷可以盛矣。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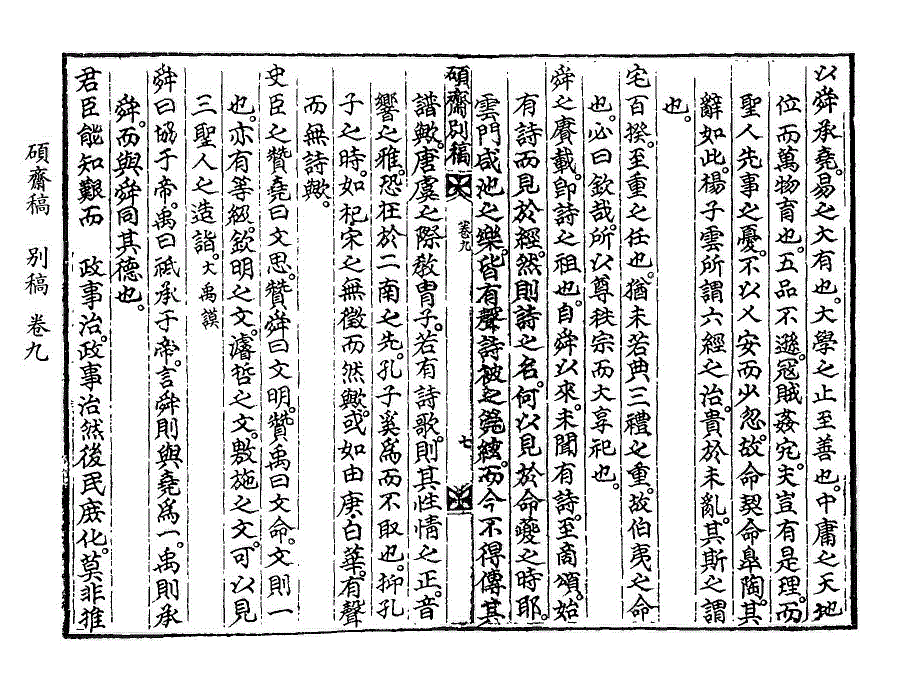 以舜承尧。易之大有也。大学之止至善也。中庸之天地位而万物育也。五品不逊。寇贼奸宄。夫岂有是理。而圣人先事之忧。不以乂安而少忽。故命契命皋陶。其辞如此。杨子云所谓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其斯之谓也。
以舜承尧。易之大有也。大学之止至善也。中庸之天地位而万物育也。五品不逊。寇贼奸宄。夫岂有是理。而圣人先事之忧。不以乂安而少忽。故命契命皋陶。其辞如此。杨子云所谓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其斯之谓也。宅百揆。至重之任也。犹未若典三礼之重。故伯夷之命也。必曰钦哉。所以尊秩宗而大享祀也。
舜之赓载。即诗之祖也。自舜以来。未闻有诗。至商颂。始有诗而见于经。然则诗之名。何以见于命夔之时耶。云门咸池之乐。皆有声诗被之筦弦。而今不得传其谱欤。唐虞之际教胄子。若有诗歌。则其性情之正。音响之雅。恐在于二南之先。孔子奚为而不取也。抑孔子之时。如杞,宋之无徵而然欤。或如由庚,白华。有声而无诗欤。
史臣之赞尧曰文思。赞舜曰文明。赞禹曰文命。文则一也。亦有等级。钦明之文。浚哲之文。敷施之文。可以见三圣人之造诣。(大禹谟)
舜曰协于帝。禹曰祗承于帝。言舜则与尧为一。禹则承舜。而与舜同其德也。
君臣能知艰而 政事治。政事治然后民庶化。莫非推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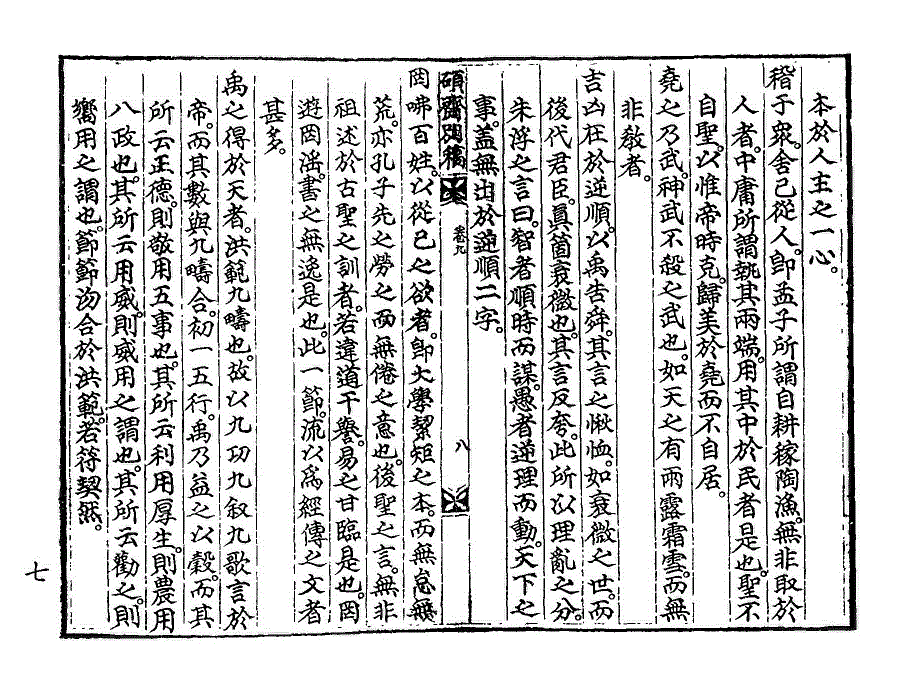 本于人主之一心。
本于人主之一心。稽于众。舍己从人。即孟子所谓自耕稼陶渔。无非取于人者。中庸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者是也。圣不自圣。以惟帝时克。归美于尧而不自居。
尧之乃武。神武不杀之武也。如天之有雨露霜雪。而无非教者。
吉凶在于逆顺。以禹告舜。其言之愀恤。如衰微之世。而后代君臣。真个衰微也。其言反夸。此所以理乱之分。朱浮之言曰。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天下之事。盖无出于逆顺二字。
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者。即大学絜矩之本。而无怠无荒。亦孔子先之劳之而无倦之意也。后圣之言。无非祖述于古圣之训者。若违道干誉。易之甘临是也。罔游罔淫。书之无逸是也。此一节。流以为经传之文者甚多。
禹之得于天者。洪范九畴也。故以九功九叙九歌言于帝。而其数与九畴合。初一五行。禹乃益之以谷。而其所云正德。则敬用五事也。其所云利用厚生。则农用八政也。其所云用威。则威用之谓也。其所云劝之。则向用之谓也。节节沕合于洪范。若符契然。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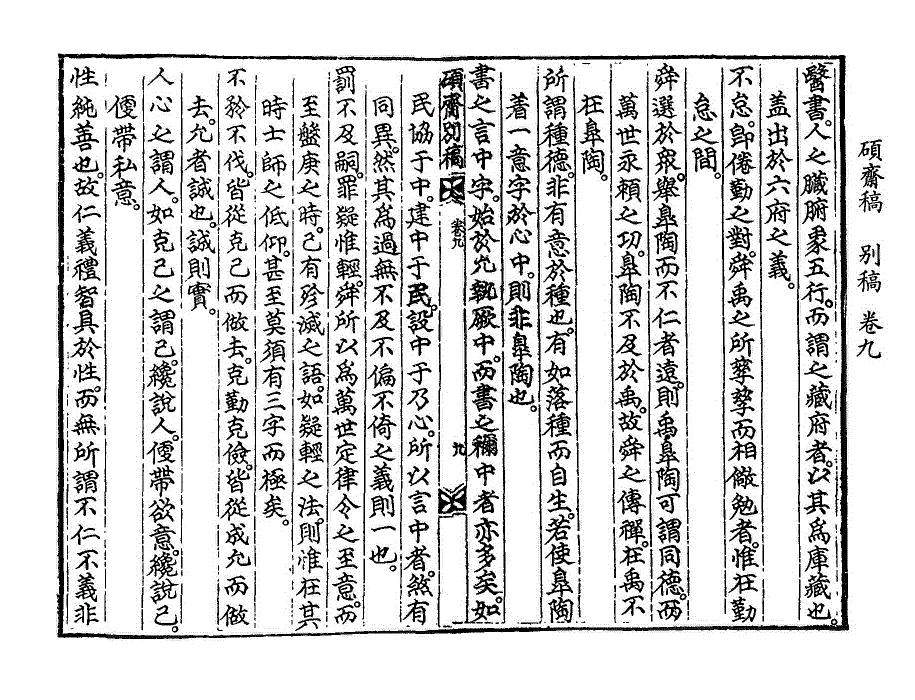 医书。人之脏腑象五行。而谓之藏府者。以其为库藏也。盖出于六府之义。
医书。人之脏腑象五行。而谓之藏府者。以其为库藏也。盖出于六府之义。不怠。即倦勤之对。舜禹之所孳孳而相儆勉者。惟在勤怠之间。
舜选于众。举皋陶而不仁者远。则禹,皋陶可谓同德。而万世永赖之功。皋陶不及于禹。故舜之传禅。在禹不在皋陶。
所谓种德。非有意于种也。有如落种而自生。若使皋陶着一意字于心中。则非皋陶也。
书之言中字。始于允执厥中。而书之称中者亦多矣。如民协于中。建中于民。设中于乃心。所以言中者。煞有同异。然其为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之义则一也。
罚不及嗣。罪疑惟轻。舜所以为万世定律令之至意。而至盘庚之时。已有殄灭之语。如疑轻之法。则惟在其时士师之低仰。甚至莫须有三字而极矣。
不矜不伐。皆从克己而做去。克勤克俭。皆从成允而做去。允者诚也。诚则实。
人心之谓人。如克己之谓己。才说人。便带欲意。才说己。便带私意。
性纯善也。故仁义礼智具于性。而无所谓不仁不义非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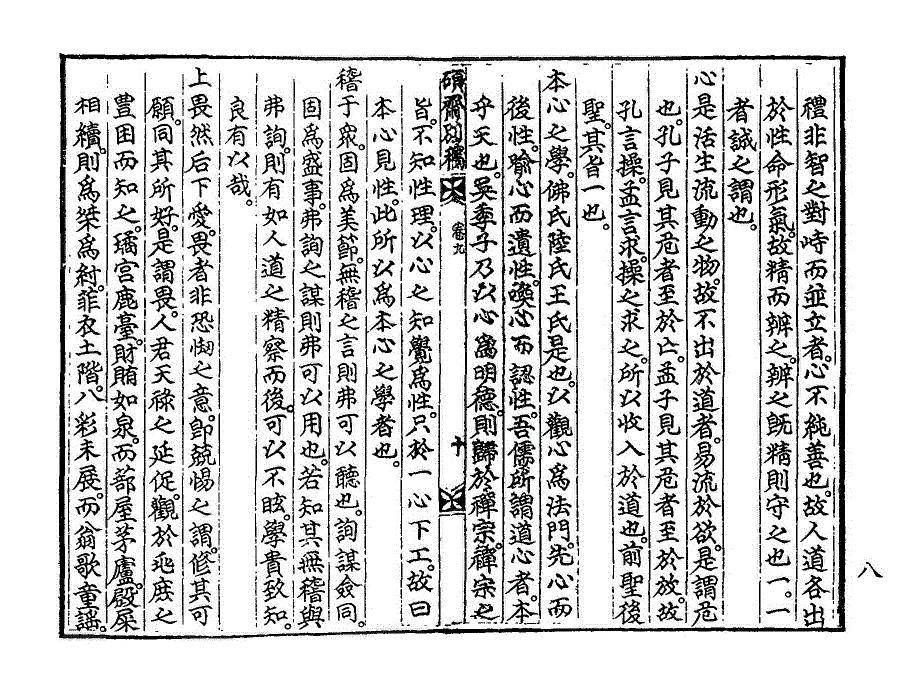 礼非智之对峙而并立者。心不纯善也。故人道各出于性命形气。故精而辨之。辨之既精则守之也一。一者诚之谓也。
礼非智之对峙而并立者。心不纯善也。故人道各出于性命形气。故精而辨之。辨之既精则守之也一。一者诚之谓也。心是活生流动之物。故不出于道者。易流于欲。是谓危也。孔子见其危者至于亡。孟子见其危者至于放。故孔言操。孟言求。操之求之。所以收入于道也。前圣后圣。其旨一也。
本心之学。佛氏陆氏王氏是也。以观心为法门。先心而后性。喻心而遗性。唤心而认性。吾儒所谓道心者。本乎天也。吴季子乃以心为明德。则归于禅宗。禅宗之旨。不知性理。以心之知觉为性。只于一心下工。故曰本心见性。此所以为本心之学者也。
稽于众。固为美节。无稽之言则弗可以听也。询谋佥同。固为盛事。弗询之谋则弗可以用也。若知其无稽与弗询。则有如人道之精察而后。可以不眩。学贵致知。良有以哉。
上畏然后下爱。畏者非恐㥘之意。即兢惕之谓。修其可愿。同其所好。是谓畏。人君天禄之延促。观于兆庶之礼困而知之。璚宫鹿台。财贿如泉。而蔀屋茅庐。殿屎相续。则为桀为纣。菲衣土阶。八彩未展。而翁歌童谣。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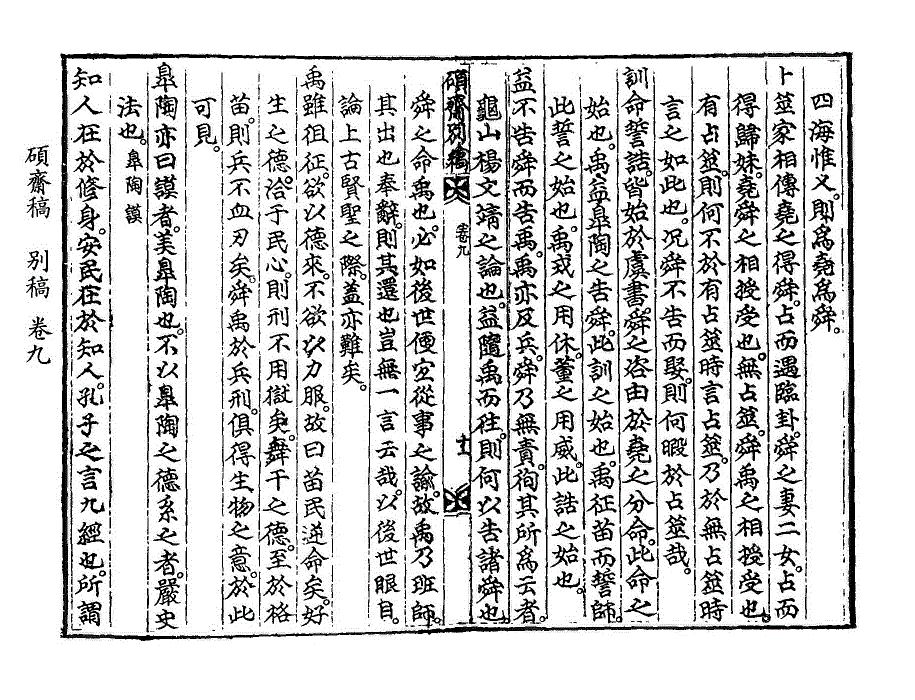 四海惟乂。则为尧为舜。
四海惟乂。则为尧为舜。卜筮家相传尧之得舜。占而遇临卦。舜之妻二女。占而得归妹。尧舜之相授受也。无占筮。舜禹之相授受也。有占筮。则何不于有占筮时言占筮。乃于无占筮时言之如此也。况舜不告而娶。则何暇于占筮哉。
训命誓诰。皆始于虞书。舜之咨由于尧之分命。此命之始也。禹,益,皋陶之告舜。此训之始也。禹征苗而誓师。此誓之始也。禹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此诰之始也。
益不告舜而告禹。禹亦反兵。舜乃无责。徇其所为云者。龟山杨文靖之论也。益随禹而往。则何以告诸舜也。舜之命禹也。必如后世便宜从事之谕。故禹乃班师。其出也奉辞。则其还也岂无一言云哉。以后世眼目。论上古贤圣之际。盖亦难矣。
禹虽徂征。欲以德来。不欲以力服。故曰苗民逆命矣。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则刑不用狱矣。舞干之德。至于格苗。则兵不血刃矣。舜禹于兵刑。俱得生物之意。于此可见。
皋陶亦曰谟者。美皋陶也。不以皋陶之德系之者。严史法也。(皋陶谟)
知人在于修身。安民在于知人。孔子之言九经也。所谓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9L 页
 思永者。致知与诚意正心并包这里。自官人至何畏乎孔壬。即大学第十章之意也。皋陶亦邻于生知之圣也。一部大学与中庸之旨。尽在于斯。
思永者。致知与诚意正心并包这里。自官人至何畏乎孔壬。即大学第十章之意也。皋陶亦邻于生知之圣也。一部大学与中庸之旨。尽在于斯。观人之法。在德不在于才。而人之所以为德者。无出于九德十八事。宽者易流。故必济之以栗。愿者易圆。故必济之以恭。盖九个十有八件。如两卦之相合而为阴阳刚柔。结之以常。即精彩所泊。常者恒也。有恒而后可久。久而后谓之吉。
日宣三德。日严祗敬六德。先儒皆以人君之所使为解者。深恐未稳。盖宣者著之称也。严者敬之谓也。又以秪敬言于九德者。所以示其用工之加密。所谓宣与严与祗与敬。皆是三德九德者所自为者。有家有邦。即在上者量其德而授其任之谓也。蔡传亦从先儒之说。恐不然。
师师二字。可见虞廷相让之本。知其贤之可师以师之。故禹让于皋陶,稷,契。伯夷让于夔,龙。而舜则翕受而敷施。此为无为之化。
皋陶始言几之一字。大有功于天下后世。阴阳消长。贤邪进退。治乱善恶。屈信动静。莫不有几。几者微也。微则难见。故审几为难。既审则研几为难。审而研之。豫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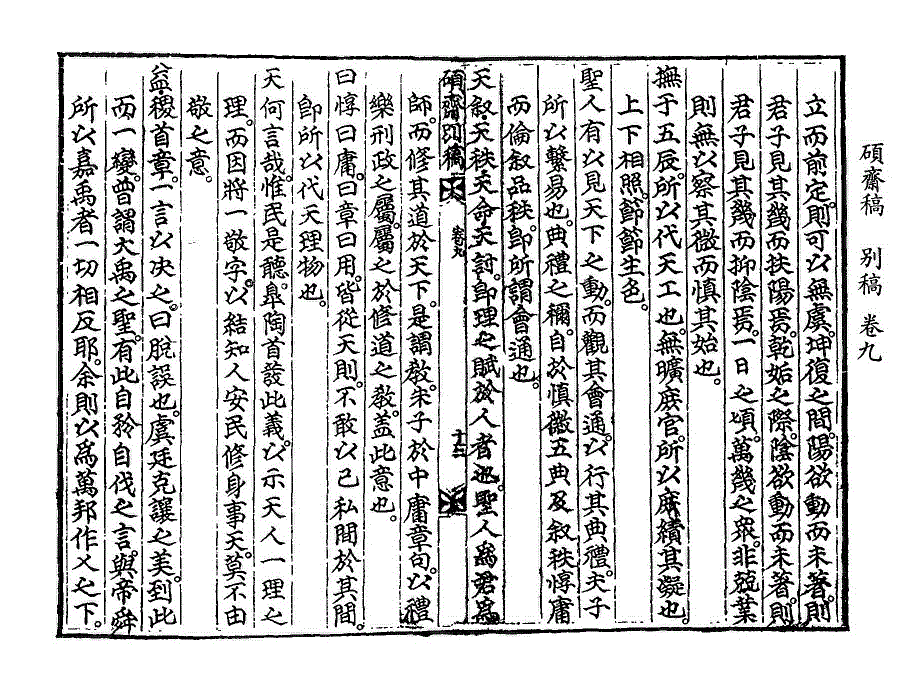 立而前定。则可以无虞。坤复之间。阳欲动而未著。则君子见其几而扶阳焉。乾姤之际。阴欲动而未著。则君子见其几而抑阴焉。一日之顷。万几之众。非兢业则无以察其微而慎其始也。
立而前定。则可以无虞。坤复之间。阳欲动而未著。则君子见其几而扶阳焉。乾姤之际。阴欲动而未著。则君子见其几而抑阴焉。一日之顷。万几之众。非兢业则无以察其微而慎其始也。抚于五辰。所以代天工也。无旷庶官。所以庶绩其凝也。上下相照。节节生色。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夫子所以系易也。典礼之称。自于慎徽五典及叙秩惇庸而伦叙品秩。即所谓会通也。
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即理之赋于人者也。圣人为君为师。而修其道于天下。是谓教。朱子于中庸章句。以礼乐刑政之属。属之于修道之教。盖此意也。
曰惇曰庸。曰章曰用。皆从天则。不敢以己私间于其间。即所以代天理物也。
天何言哉。惟民是听。皋陶首发此义。以示天人一理之理。而因将一敬字。以结知人安民修身事天。莫不由敬之意。
益,稷首章。一言以决之。曰脱误也。虞廷克让之美。到此而一变。曾谓大禹之圣。有此自矜自伐之言。与帝舜所以嘉禹者一切相反耶。余则以为万邦作乂之下。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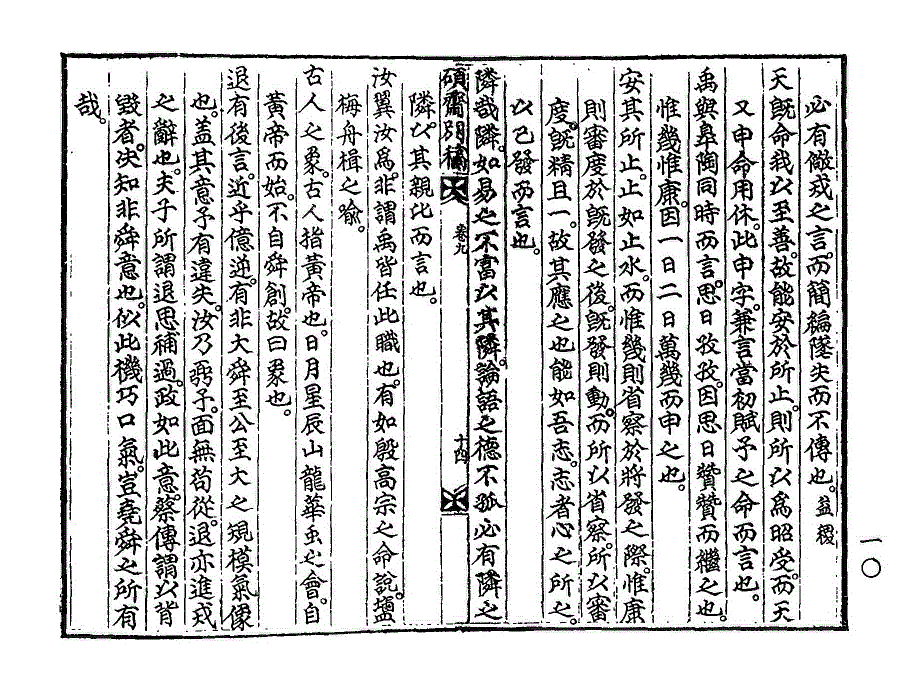 必有儆戒之言。而简编坠失而不传也。(益稷)
必有儆戒之言。而简编坠失而不传也。(益稷)天既命我以至善。故能安于所止。则所以为昭受。而天又申命用休。此申字。兼言当初赋予之命而言也。
禹与皋陶同时而言。思日孜孜。因思日赞赞而继之也。惟几惟康。因一日二日万几而申之也。
安其所止。止如止水。而惟几则省察于将发之际。惟康则审度于既发之后。既发则动。而所以省察。所以审度。既精且一。故其应之也能如吾志。志者心之所之。以已发而言也。
邻哉邻。如易之不富以其邻。论语之德不孤必有邻之邻。以其亲比而言也。
汝翼汝为。非谓禹皆任此职也。有如殷高宗之命说。盐梅舟楫之喻。
古人之象。古人指黄帝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之会。自黄帝而始。不自舜创。故曰象也。
退有后言。近乎亿逆。有非大舜至公至大之规模气像也。盖其意予有违失。汝乃弼予。面无苟从。退亦进戒之辞也。夫子所谓退思补过。政如此意。蔡传谓以背毁者。决知非舜意也。似此机巧口气。岂尧舜之所有哉。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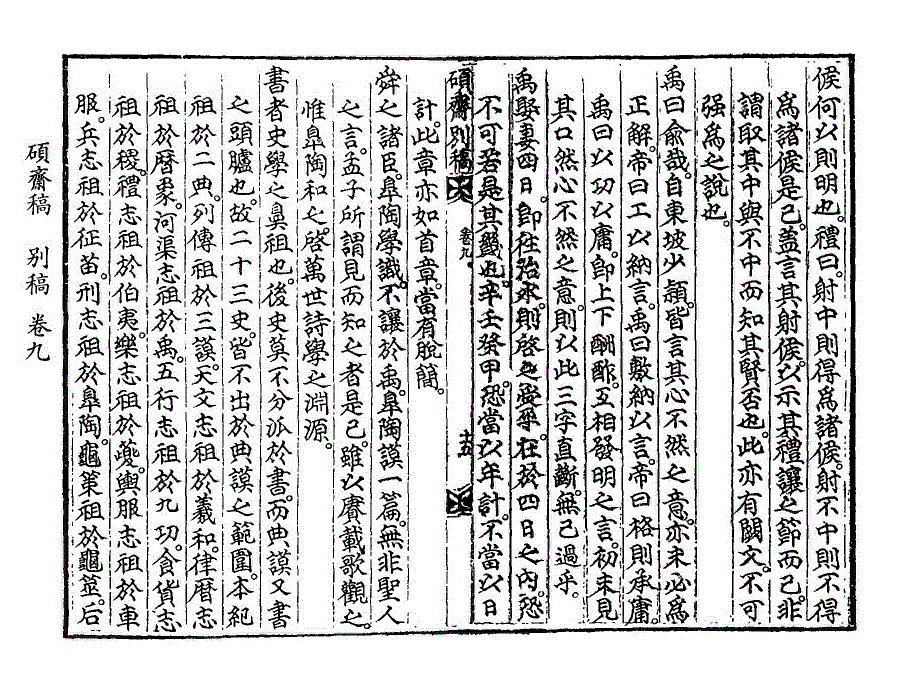 侯何以则明也。礼曰。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是已。盖言其射侯。以示其礼让之节而已。非谓取其中与不中而知其贤否也。此亦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也。
侯何以则明也。礼曰。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是已。盖言其射侯。以示其礼让之节而已。非谓取其中与不中而知其贤否也。此亦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也。禹曰俞哉。自东坡少颖。皆言其心不然之意。亦未必为正解。帝曰工以纳言。禹曰敷纳以言。帝曰格则承庸。禹曰以功以庸。即上下酬酢。互相发明之言。初未见其口然心不然之意。则以此三字直断。无已过乎。
禹娶妻四日。即往治水。则启之受孕。在于四日之内。恐不可若是其几也。辛壬癸甲。恐当以年计。不当以日计。此章亦如首章。当有脱简。
舜之诸臣。皋陶学识。不让于禹。皋陶谟一篇。无非圣人之言。孟子所谓见而知之者是已。虽以赓载歌观之。惟皋陶和之。启万世诗学之渊源。
书者史学之鼻祖也。后史莫不分派于书。而典谟又书之头胪也。故二十三史。皆不出于典谟之范围。本纪祖于二典。列传祖于三谟。天文志祖于羲和。律历志祖于历象。河渠志祖于禹。五行志祖于九功。食货志祖于稷。礼志祖于伯夷。乐志祖于夔。舆服志祖于车服。兵志祖于征苗。刑志祖于皋陶。龟策祖于龟筮。后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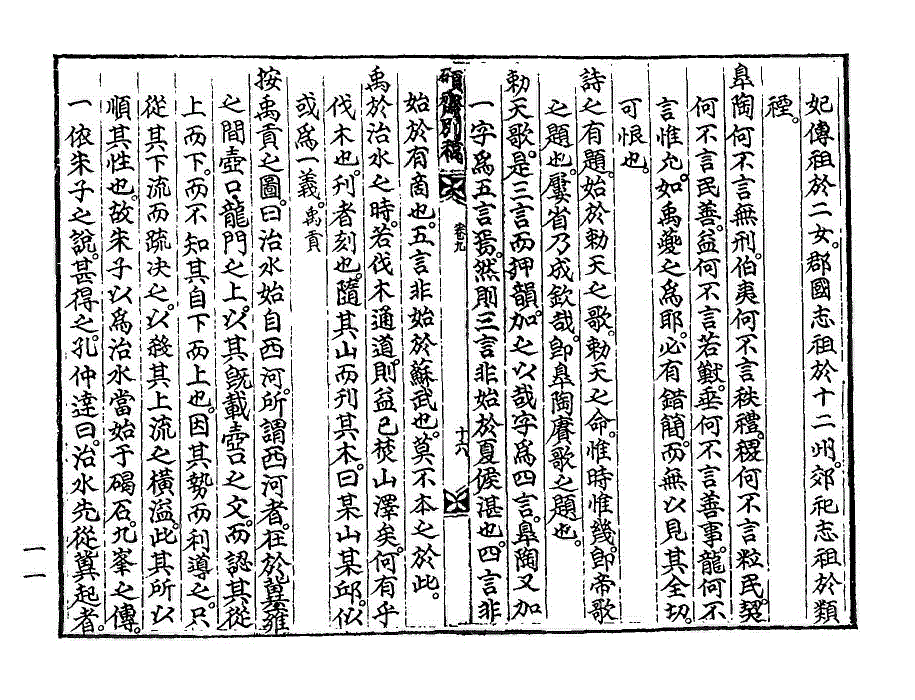 妃传祖于二女。郡国志祖于十二州。郊祀志祖于类禋。
妃传祖于二女。郡国志祖于十二州。郊祀志祖于类禋。皋陶何不言无刑。伯夷何不言秩礼。稷何不言粒民。契何不言民善。益何不言若兽。垂何不言善事。龙何不言惟允。如禹夔之为耶。必有错简。而无以见其全切。可恨也。
诗之有题。始于敕天之歌。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即帝歌之题也。屡省乃成钦哉。即皋陶赓歌之题也。
敕天歌。是三言而押韵。加之以哉字为四言。皋陶又加一字为五言焉。然则三言非始于夏侯湛也。四言非始于有商也。五言非始于苏武也。莫不本之于此。
禹于治水之时。若伐木通道。则益已焚山泽矣。何有乎伐木也。刊者刻也。随其山而刊其木。曰某山某邱。似或为一义。(禹贡)
按禹贡之图。曰治水始自西河。所谓西河者。在于冀,雍之间壶口,龙门之上。以其既载壶口之文。而认其从上而下。而不知其自下而上也。因其势而利导之。只从其下流而疏决之。以杀其上流之横溢。此其所以顺其性也。故朱子以为治水当始于碣石。九峰之传。一依朱子之说。甚得之。孔仲达曰。治水先从冀起者。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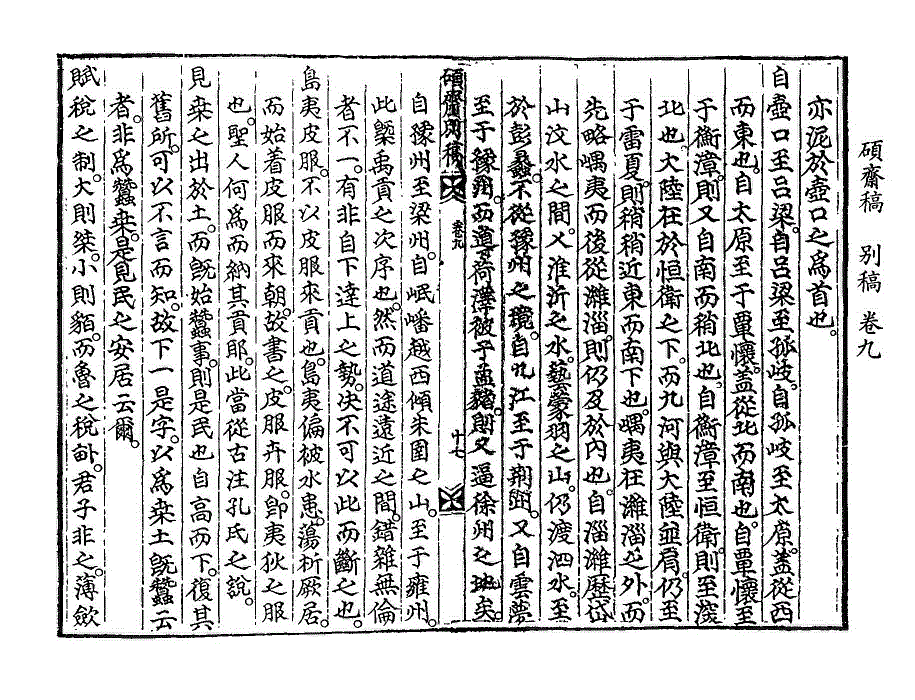 亦泥于壶口之为首也。
亦泥于壶口之为首也。自壶口至吕梁。自吕梁至孤岐。自孤岐至太原。盖从西而东也。自太原至于覃怀。盖从北而南也。自覃怀至于衡漳。则又自南而稍北也。自衡漳至恒卫。则至深北也。大陆在于恒卫之下。而九河与大陆并肩。仍至于雷夏。则稍稍近东而南下也。嵎夷在潍淄之外。而先略嵎夷而后从潍淄。则仍及于内也。自淄潍历岱山汶水之间。乂淮沂之水。艺蒙羽之山。仍渡泗水。至于彭蠡。不从豫州之境。自九江至于荆州。又自云梦至于豫州。而导荷泽被于孟猪。则又逼徐州之地矣。自豫州至梁州。自岷嶓越西倾朱圉之山。至于雍州。此槩禹贡之次序也。然而道途远近之间。错杂无伦者不一。有非自下达上之势。决不可以此而断之也。
岛夷皮服。不以皮服来贡也。岛夷偏被水患。荡析厥居。而始着皮服而来朝。故书之。皮服卉服。即夷狄之服也。圣人何为而纳其贡耶。此当从古注孔氏之说。
见桑之出于土。而既始蚕事。则是民也自高而下。复其旧所。可以不言而知。故下一是字。以为桑土既蚕云者。非为蚕桑。是见民之安居云尔。
赋税之制。大则桀。小则貊。而鲁之税亩。君子非之。薄敛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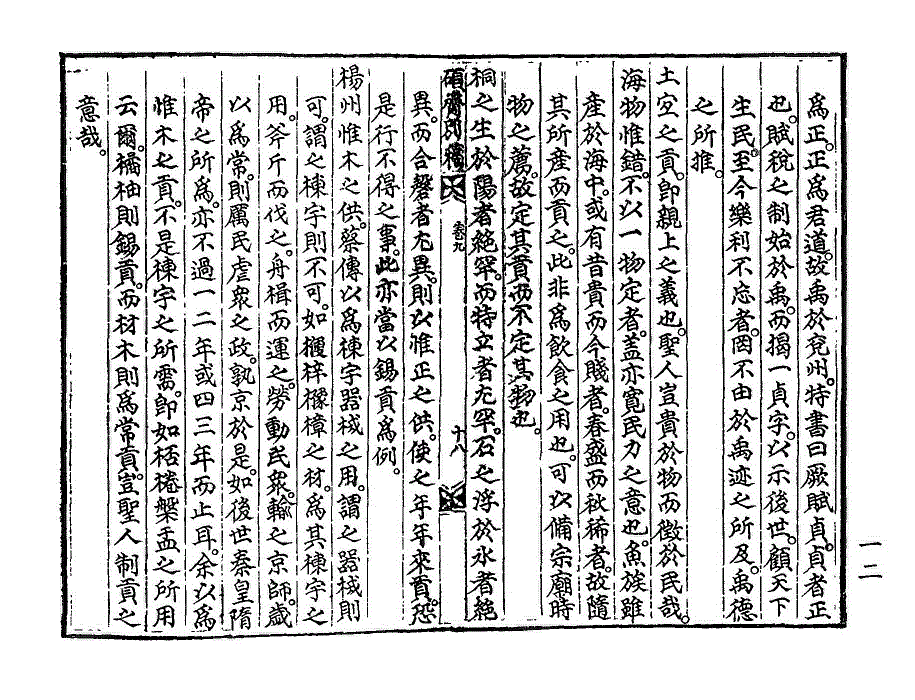 为正。正为君道。故禹于兖州。特书曰厥赋贞。贞者正也。赋税之制始于禹。而揭一贞字。以示后世。顾天下生民。至今乐利不忘者。罔不由于禹迹之所及。禹德之所推。
为正。正为君道。故禹于兖州。特书曰厥赋贞。贞者正也。赋税之制始于禹。而揭一贞字。以示后世。顾天下生民。至今乐利不忘者。罔不由于禹迹之所及。禹德之所推。土宜之贡。即亲上之义也。圣人岂贵于物而徵于民哉。
海物惟错。不以一物定者。盖亦宽民力之意也。鱼族虽产于海中。或有昔贵而今贱者。春盛而秋稀者。故随其所产而贡之。此非为饮食之用也。可以备宗庙时物之荐。故定其贡而不定其物也。
桐之生于阳者绝罕。而特立者尤罕。石之浮于冰者绝异。而合磬者尤异。则以惟正之供。使之年年来贡。恐是行不得之事。此亦当以锡贡为例。
杨州惟木之供。蔡传以为栋宇器械之用。谓之器械则可。谓之栋宇则不可。如楩梓櫲樟之材。为其栋宇之用。斧斤而伐之。舟楫而运之。劳动民众。输之京师。岁以为常。则厉民虐众之政。孰京于是。如后世秦皇隋帝之所为。亦不过一二年或四三年而止耳。余以为惟木之贡。不是栋宇之所需。即如杯棬槃盂之所用云尔。橘柚则锡贡。而材木则为常贡。岂圣人制贡之意哉。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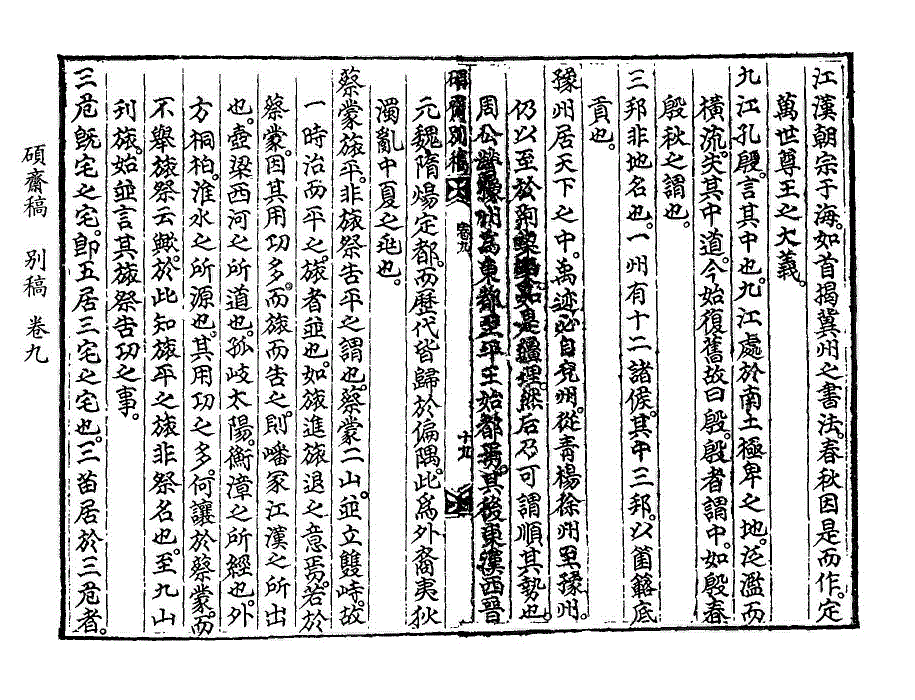 江汉朝宗于海。如首揭冀州之书法。春秋因是而作。定万世尊王之大义。
江汉朝宗于海。如首揭冀州之书法。春秋因是而作。定万世尊王之大义。九江孔殷。言其中也。九江处于南土极卑之地。泛滥而横流。失其中道。今始复旧故曰殷。殷者谓中。如殷春殷秋之谓也。
三邦非地名也。一州有十二诸侯。其中三邦。以箘簬底贡也。
豫州居天下之中。禹迹必自兖州。从青杨徐州至豫州。仍以至于荆梁幽(一作雍)。如是疆理。然后乃可谓顺其势也。周公营豫州为东都。至平王始都焉。其后东汉西晋元魏,隋炀定都。而历代皆归于偏隅。此为外裔夷狄浊乱中夏之兆也。
蔡蒙旅平。非旅祭告平之谓也。蔡蒙二山。并立双峙。故一时治而平之。旅者并也。如旅进旅退之意焉。若于蔡蒙。因其用功多。而旅而告之。则嶓冢江汉之所出也。壶梁西河之所道也。孤岐太阳。衡漳之所经也。外方桐柏。淮水之所源也。其用功之多。何让于蔡蒙。而不举旅祭云欤。于此知旅平之旅非祭名也。至九山刊旅。始并言其旅祭告功之事。
三危既宅之宅。即五居三宅之宅也。三苗居于三危者。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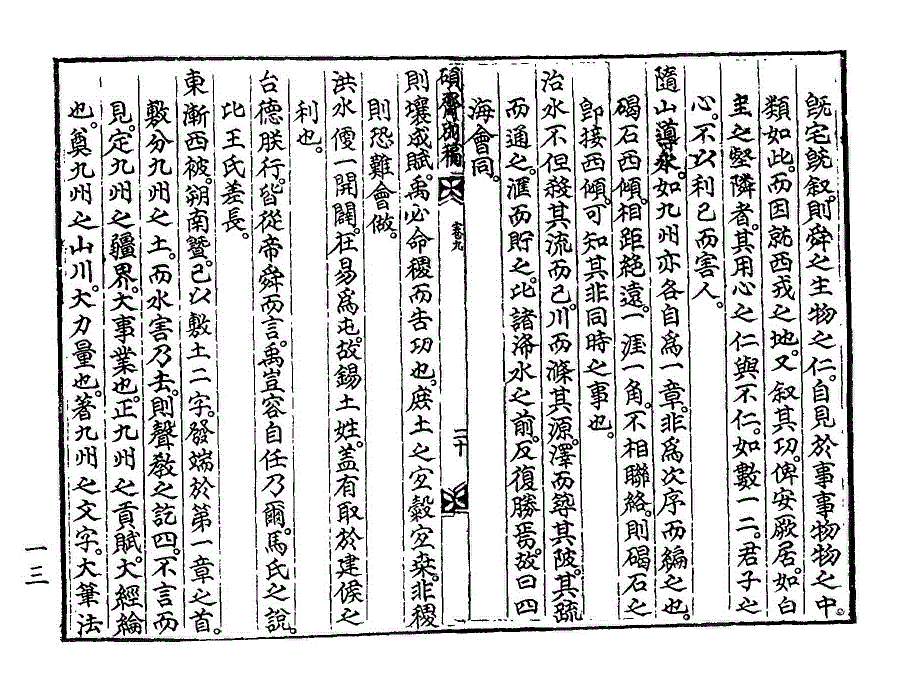 既宅既叙。则舜之生物之仁。自见于事事物物之中。类如此。而因就西戎之地。又叙其功。俾安厥居。如白圭之壑邻者。其用心之仁与不仁。如数一二。君子之心。不以利己而害人。
既宅既叙。则舜之生物之仁。自见于事事物物之中。类如此。而因就西戎之地。又叙其功。俾安厥居。如白圭之壑邻者。其用心之仁与不仁。如数一二。君子之心。不以利己而害人。随山导水。如九州亦各自为一章。非为次序而编之也。碣石西倾。相距绝远。一涯一角。不相联络。则碣石之即接西倾。可知其非同时之事也。
治水不但杀其流而已。川而涤其源。泽而筑其陂。其疏而通之。汇而贮之。比诸洚水之前。反复胜焉。故曰四海会同。
则壤成赋。禹必命稷而告功也。庶土之宜谷宜桑。非稷则恐难会做。
洪水便一开辟。在易为屯。故锡土姓。盖有取于建侯之利也。
台德朕行。皆从帝舜而言。禹岂容自任乃尔。马氏之说。比王氏差长。
东渐西被。朔南暨。已以敷土二字。发端于第一章之首。敷分九州之土。而水害乃去。则声教之讫四。不言而见。定九州之疆界。大事业也。正九州之贡赋。大经纶也。奠九州之山川。大力量也。著九州之文字。大笔法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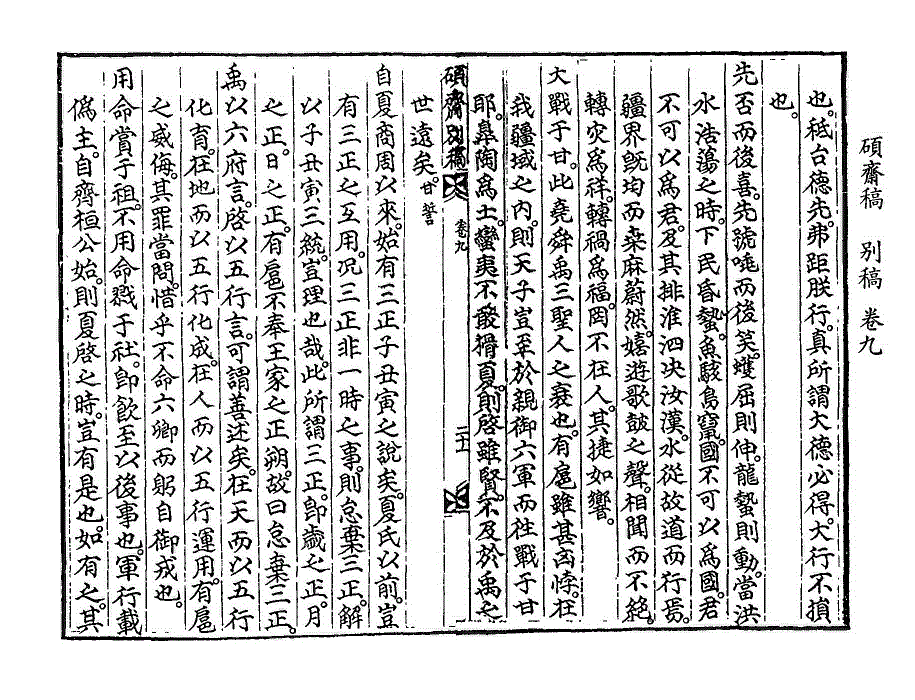 也。秪台德先。弗距朕行。真所谓大德必得。大行不损也。
也。秪台德先。弗距朕行。真所谓大德必得。大行不损也。先否而后喜。先号咷而后笑。蠖屈则伸。龙蛰则动。当洪水浩荡之时。下民昏蛰。鱼骇鸟窜。国不可以为国。君不可以为君。及其排淮泗决汝汉。水从故道而行焉。疆界既均而桑麻蔚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而不绝。转灾为祥。转祸为福。罔不在人。其捷如响。
大战于甘。此尧舜禹三圣人之衰也。有扈虽甚凶悖。在我疆域之内。则天子岂至于亲御六军而往战于甘耶。皋陶为士。蛮夷不敢猾夏。则启虽贤。不及于禹之世远矣。(甘誓)
自夏商周以来。始有三正子丑寅之说矣。夏氏以前。岂有三正之互用。况三正非一时之事。则怠弃三正。解以子丑寅三统。岂理也哉。此所谓三正。即岁之正。月之正。日之正。有扈不奉王家之正朔。故曰怠弃三正。
禹以六府言。启以五行言。可谓善述矣。在天而以五行化育。在地而以五行化成。在人而以五行运用。有扈之威侮。其罪当问。惜乎不命六卿而躬自御戎也。
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即饮至以后事也。军行载伪主。自齐桓公始。则夏启之时。岂有是也。如有之。其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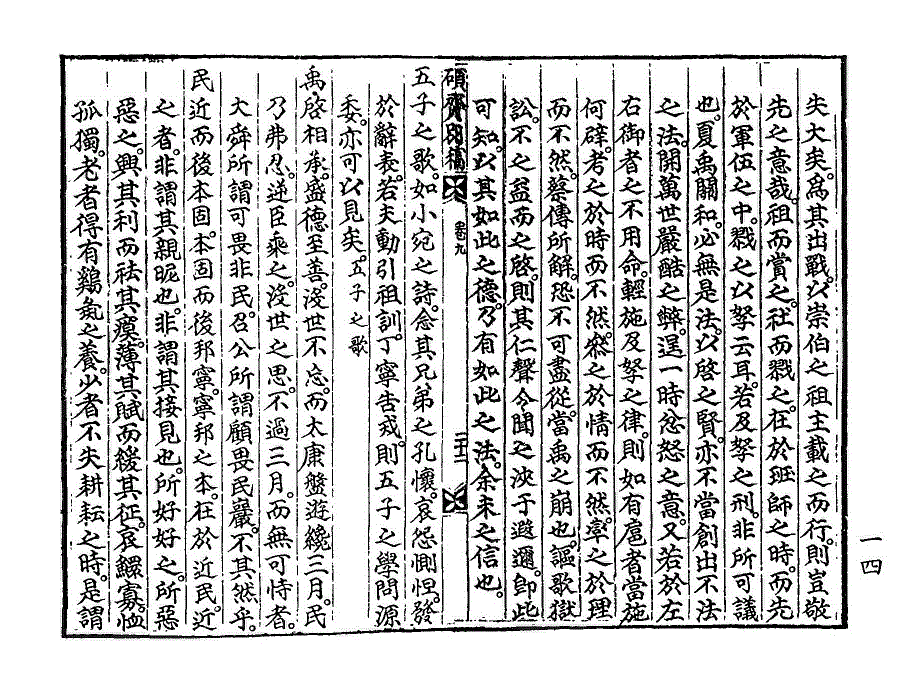 失大矣。为其出战。以崇伯之祖主载之而行。则岂敬先之意哉。祖而赏之。社而戮之。在于班师之时。而先于军伍之中。戮之以孥云耳。若及孥之刑。非所可议也。夏禹关和。必无是法。以启之贤。亦不当创出不法之法。开万世严酷之弊。逞一时忿怒之意。又若于左右御者之不用命。轻施及孥之律。则如有扈者当施何辟。考之于时而不然。参之于情而不然。率之于理而不然。蔡传所解。恐不可尽从。当禹之崩也。讴歌狱讼。不之益而之启。则其仁声令闻之浃于遐迩。即此可知。以其如此之德。乃有如此之法。余未之信也。
失大矣。为其出战。以崇伯之祖主载之而行。则岂敬先之意哉。祖而赏之。社而戮之。在于班师之时。而先于军伍之中。戮之以孥云耳。若及孥之刑。非所可议也。夏禹关和。必无是法。以启之贤。亦不当创出不法之法。开万世严酷之弊。逞一时忿怒之意。又若于左右御者之不用命。轻施及孥之律。则如有扈者当施何辟。考之于时而不然。参之于情而不然。率之于理而不然。蔡传所解。恐不可尽从。当禹之崩也。讴歌狱讼。不之益而之启。则其仁声令闻之浃于遐迩。即此可知。以其如此之德。乃有如此之法。余未之信也。五子之歌。如小宛之诗。念其兄弟之孔怀。哀怨恻怛。发于辞表。若夫动引祖训。丁宁告戒。则五子之学问源委。亦可以见矣。(五子之歌)
禹,启相承。盛德至善。没世不忘。而太康盘游才三月。民乃弗忍。逆臣乘之。没世之思。不过三月。而无可恃者。大舜所谓可畏非民。召公所谓顾畏民岩。不其然乎。
民近而后本固。本固而后邦宁。宁邦之本。在于近民。近之者。非谓其亲昵也。非谓其接见也。所好好之。所恶恶之。兴其利而祛其瘼。薄其赋而缓其征。哀鳏寡。恤孤独。老者得有鸡彘之养。少者不失耕耘之时。是谓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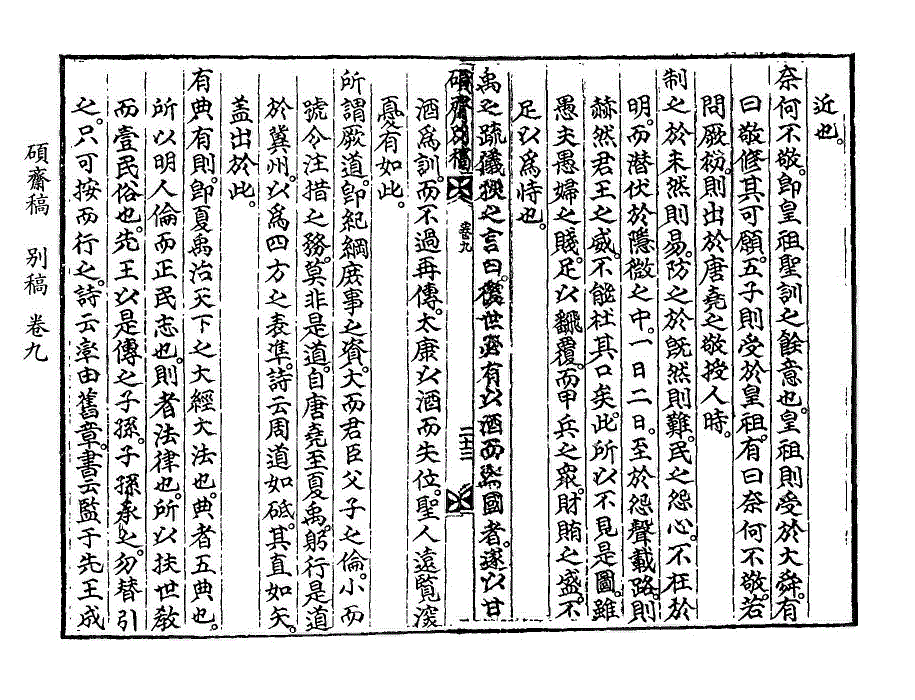 近也。
近也。奈何不敬。即皇祖圣训之馀意也。皇祖则受于大舜。有曰敬修其可愿。五子则受于皇祖。有曰奈何不敬。若问厥初。则出于唐尧之敬授人时。
制之于未然则易。防之于既然则难。民之怨心。不在于明。而潜伏于隐微之中。一日二日。至于怨声载路。则赫然君王之威。不能杜其口矣。此所以不见是图。虽愚夫愚妇之贱。足以翻覆。而甲兵之众。财贿之盛。不足以为恃也。
禹之疏仪狄之言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遂以甘酒为训。而不过再传。太康以酒而失位。圣人远览深忧有如此。
所谓厥道。即纪纲庶事之资。大而君臣父子之伦。小而号令注措之务。莫非是道。自唐尧至夏禹。躬行是道于冀州。以为四方之表准。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盖出于此。
有典有则。即夏禹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典者五典也。所以明人伦而正民志也。则者法律也。所以扶世教而壹民俗也。先王以是传之子孙。子孙承之。勿替引之。只可按而行之。诗云率由旧章。书云监于先王成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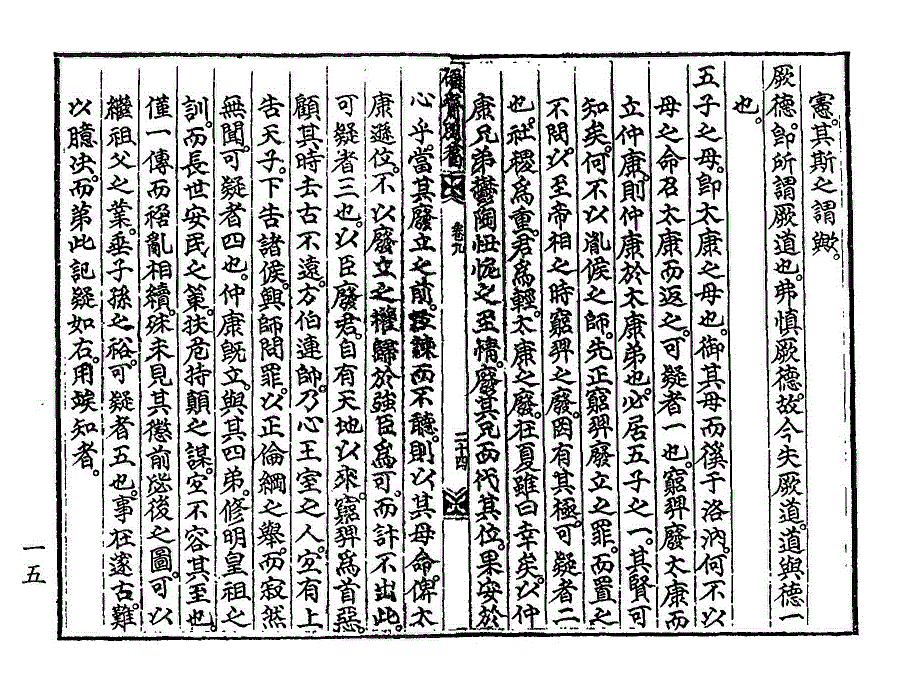 宪。其斯之谓欤。
宪。其斯之谓欤。厥德。即所谓厥道也。弗慎厥德。故今失厥道。道与德一也。
五子之母。即太康之母也。御其母而徯于洛汭。何不以母之命召太康而返之。可疑者一也。穷羿废太康而立仲康。则仲康于太康弟也。必居五子之一。其贤可知矣。何不以胤侯之师。先正穷羿废立之罪。而置之不问。以至帝相之时穷羿之废。罔有其极。可疑者二也。社稷为重。君为轻。太康之废。在夏虽曰幸矣。以仲康兄弟郁陶忸怩之至情。废其兄而代其位。果安于心乎。当其废立之前。泣谏而不听。则以其母命。俾太康逊位。不以废立之权归于强臣为可。而计不出此。可疑者三也。以臣废君。自有天地以来。穷羿为首恶。顾其时去古不远。方伯连帅。乃心王室之人。宜有上告天子。下告诸侯。兴师问罪。以正伦纲之举。而寂然无闻。可疑者四也。仲康既立。与其四弟。修明皇祖之训。而长世安民之策。扶危持颠之谋。宜不容其至也。仅一传而𥙯乱相续。殊未见其惩前毖后之图。可以继祖父之业。垂子孙之裕。可疑者五也。事在邃古。难以臆决。而第此记疑如右。用俟知者。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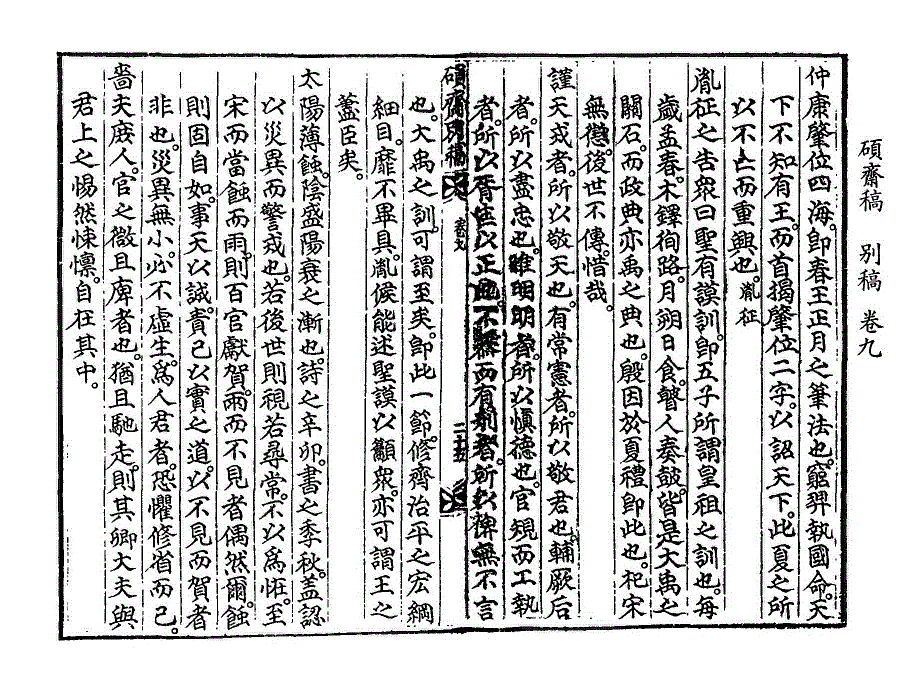 仲康肇位四海。即春王正月之笔法也。穷羿执国命。天下不知有王。而首揭肇位二字。以诏天下。此夏之所以不亡而重兴也。(胤征)
仲康肇位四海。即春王正月之笔法也。穷羿执国命。天下不知有王。而首揭肇位二字。以诏天下。此夏之所以不亡而重兴也。(胤征)胤征之告众曰圣有谟训。即五子所谓皇祖之训也。每岁孟春。木铎徇路。月朔日食。𥌒人奏鼓。皆是大禹之关石。而政典亦禹之典也。殷因于夏礼即此也。杞宋无惩。后世不传。惜哉。
谨天戒者。所以敬天也。有常宪者。所以敬君也。辅厥后者。所以尽忠也。惟明明者。所以慎德也。官规而工执者。所以胥匡以正也。不恭而有刑者。所以俾无不言也。大禹之训。可谓至矣。即此一节。修齐治平之宏纲细目。靡不毕具。胤侯能述圣谟以吁众。亦可谓王之荩臣矣。
太阳薄蚀。阴盛阳衰之渐也。诗之辛卯。书之季秋。盖认以灾异而警戒也。若后世则视若寻常。不以为怪。至宋而当蚀而雨。则百官献贺。雨而不见者偶然尔。蚀则固自如。事天以诚。责己以实之道。以不见而贺者非也。灾异无小。必不虚生。为人君者。恐惧修省而已。
啬夫庶人。官之微且庳者也。犹且驰走。则其卿大夫与君上之惕然悚懔。自在其中。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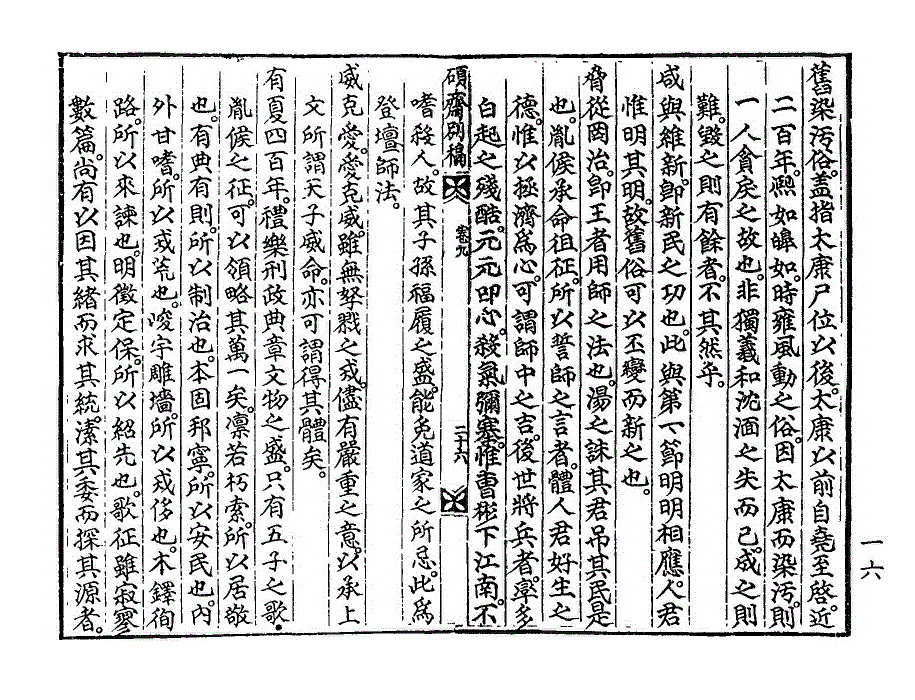 旧染污俗。盖指太康尸位以后。太康以前自尧至启。近二百年。熙如皞如。时雍风动之俗。因太康而染污。则一人贪戾之故也。非独羲和沈湎之失而已。成之则难。毁之则有馀者。不其然乎。
旧染污俗。盖指太康尸位以后。太康以前自尧至启。近二百年。熙如皞如。时雍风动之俗。因太康而染污。则一人贪戾之故也。非独羲和沈湎之失而已。成之则难。毁之则有馀者。不其然乎。咸与维新。即新民之功也。此与第一节明明相应。人君惟明其明。故旧俗可以丕变而新之也。
胁从罔治。即王者用师之法也。汤之诛其君吊其民是也。胤侯承命徂征。所以誓师之言者。体人君好生之德。惟以拯济为心。可谓师中之吉。后世将兵者。率多白起之残酷。元元叩心。杀气弥塞。惟曹彬下江南。不嗜杀人。故其子孙福履之盛。能免道家之所忌。此为登坛师法。
威克爱。爱克威。虽无孥戮之戒。尽有严重之意。以承上文所谓天子威命。亦可谓得其体矣。
有夏四百年。礼乐刑政典章文物之盛。只有五子之歌,胤侯之征。可以领略其万一矣。凛若朽索。所以居敬也。有典有则。所以制治也。本固邦宁。所以安民也。内外甘嗜。所以戒荒也。峻宇雕墙。所以戒侈也。木铎徇路。所以来谏也。明徵定保。所以绍先也。歌征虽寂寥数篇。尚有以因其绪而求其统。溸其委而探其源者。
硕斋别稿卷之九 第 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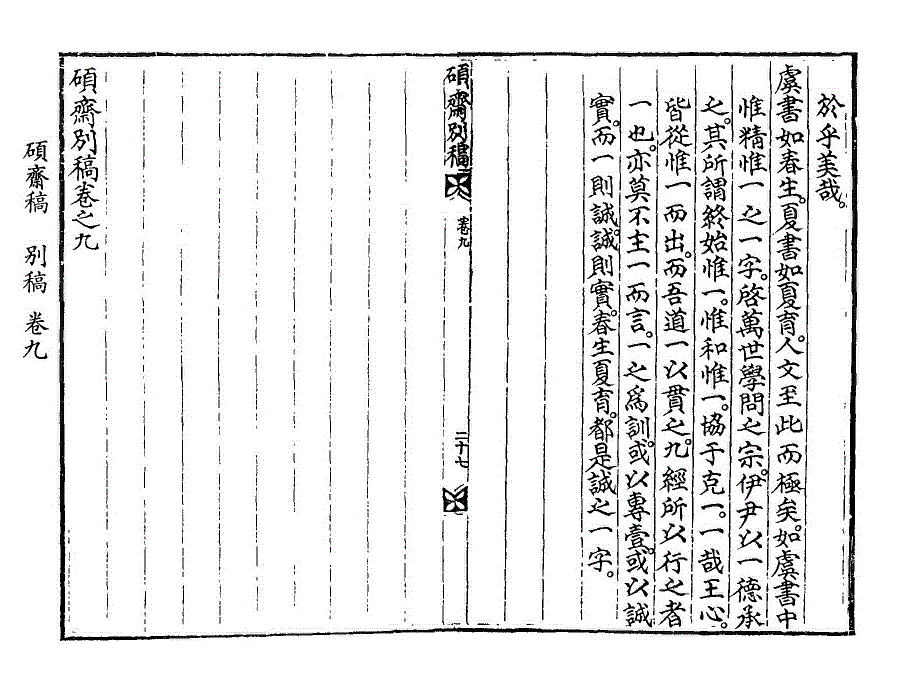 于乎美哉。
于乎美哉。虞书如春生。夏书如夏育。人文至此而极矣。如虞书中惟精惟一之一字。启万世学问之宗。伊尹以一德承之。其所谓终始惟一。惟和惟一。协于克一。一哉王心。皆从惟一而出。而吾道一以贯之。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亦莫不主一而言。一之为训。或以专壹。或以诚实。而一则诚。诚则实。春生夏育。都是诚之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