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四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读孟子至万章篇。而尊王道。黜霸术。遏人欲。存天理。如承警咳于左右。恍然如见磊落光明之气像。余小子若读此书。而不能体悉于求仁行义之旨。则真孟子所谓自㬥自弃者也。仍始告子篇以下。遂书此以自警。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读孟子至万章篇。而尊王道。黜霸术。遏人欲。存天理。如承警咳于左右。恍然如见磊落光明之气像。余小子若读此书。而不能体悉于求仁行义之旨。则真孟子所谓自㬥自弃者也。仍始告子篇以下。遂书此以自警。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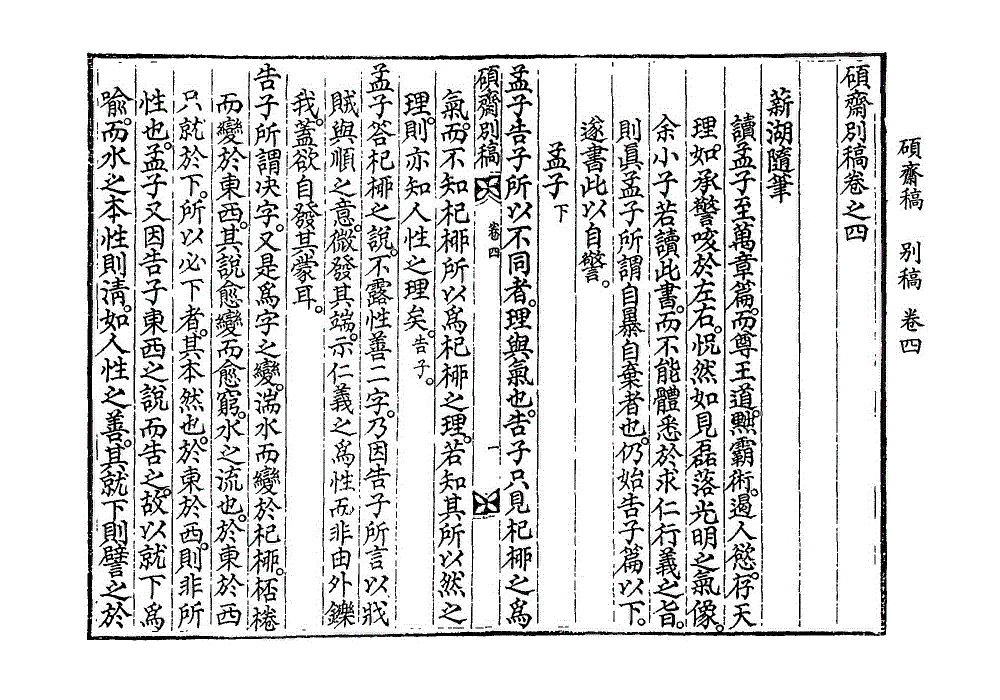 孟子[下]
孟子[下]孟子,告子所以不同者。理与气也。告子只见杞柳之为气。而不知杞柳所以为杞柳之理。若知其所以然之理。则亦知人性之理矣。(告子。)
孟子答杞柳之说。不露性善二字。乃因告子所言以戕贼与顺之意。微发其端。示仁义之为性而非由外铄我。盖欲自发其蒙耳。
告子所谓决字。又是为字之变。湍水而变于杞柳。杯棬而变于东西。其说愈变而愈穷。水之流也。于东于西只就于下。所以必下者。其本然也。于东于西。则非所性也。孟子又因告子东西之说而告之。故以就下为喻。而水之本性则清。如人性之善。其就下则譬之于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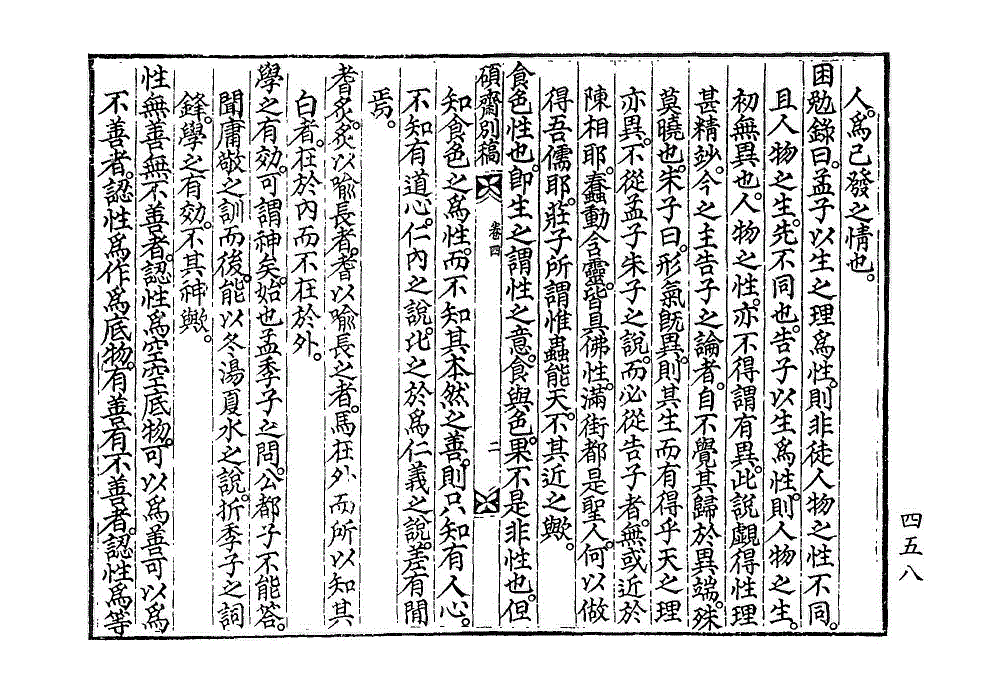 人。为已发之情也。
人。为已发之情也。困勉录曰。孟子以生之理为性。则非徒人物之性不同。且人物之生。先不同也。告子以生为性。则人物之生。初无异也。人物之性。亦不得谓有异。此说觑得性理甚精妙。今之主告子之论者。自不觉其归于异端。殊莫晓也。朱子曰。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不从孟子朱子之说。而必从告子者。无或近于陈相耶。蠢动含灵。皆具佛性。满街都是圣人。何以做得吾儒耶。庄子所谓惟虫能天。不其近之欤。
食色性也。即生之谓性之意。食与色。果不是非性也。但知食色之为性。而不知其本然之善。则只知有人心。不知有道心。仁内之说。比之于为仁义之说。差有閒焉。
耆炙。炙以喻长者。耆以喻长之者。马在外而所以知其白者。在于内而不在于外。
学之有效。可谓神矣。始也孟季子之问。公都子不能答。闻庸敬之训而后。能以冬汤夏水之说。折季子之词锋。学之有效。不其神欤。
性无善无不善者。认性为空空底物。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者。认性为作为底物。有善有不善者。认性为等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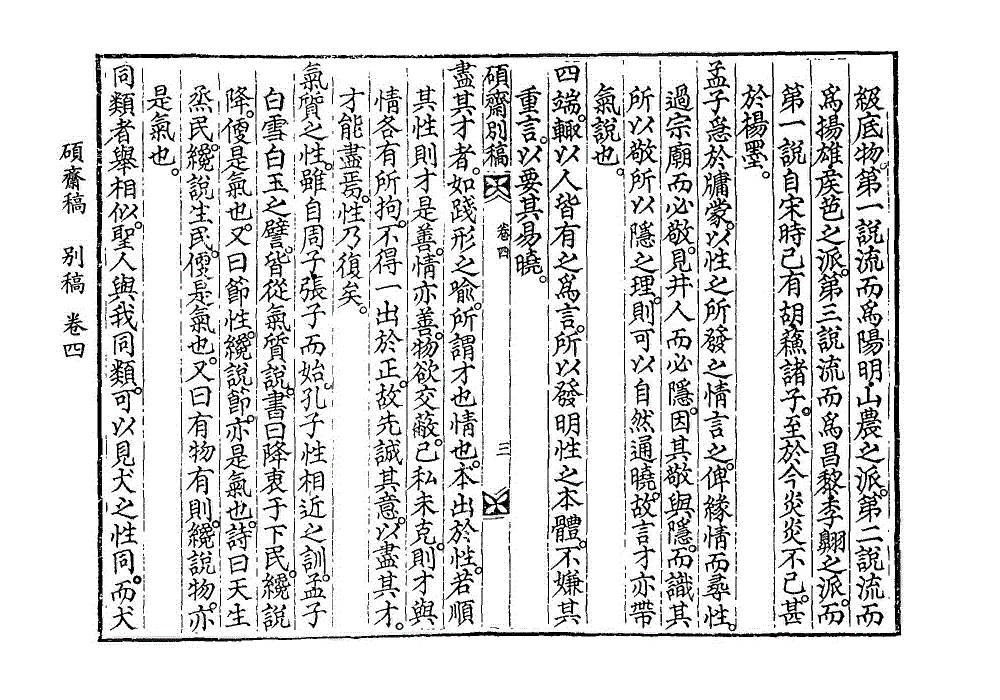 级底物。第一说流而为阳明,山农之派。第二说流而为扬雄,侯芭之派。第三说流而为昌黎,李翱之派。而第一说自宋时已有胡,苏诸子。至于今炎炎不已。甚于杨墨。
级底物。第一说流而为阳明,山农之派。第二说流而为扬雄,侯芭之派。第三说流而为昌黎,李翱之派。而第一说自宋时已有胡,苏诸子。至于今炎炎不已。甚于杨墨。孟子急于牖蒙。以性之所发之情言之。俾缘情而寻性。过宗庙而必敬。见井人而必隐。因其敬与隐。而识其所以敬所以隐之理。则可以自然通晓。故言才亦带气说也。
四端。辄以人皆有之为言。所以发明性之本体。不嫌其重言。以要其易晓。
尽其才者。如践形之喻。所谓才也情也。本出于性。若顺其性则才是善。情亦善。物欲交蔽。己私未克。则才与情各有所拘。不得一出于正。故先诚其意。以尽其才。才能尽焉。性乃复矣。
气质之性。虽自周子,张子而始。孔子性相近之训。孟子白雪白玉之譬。皆从气质说。书曰降衷于下民。才说降。便是气也。又曰节性。才说节。亦是气也。诗曰天生烝民。才说生民。便是气也。又曰有物有则。才说物。亦是气也。
同类者举相似。圣人与我同类。可以见犬之性同。而犬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59L 页
 不与牛性同。牛之性同。而牛不与犬性同。人之性同而不与犬牛同之理也。故曰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
不与牛性同。牛之性同。而牛不与犬性同。人之性同而不与犬牛同之理也。故曰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以其万事万物。理无不在。一动一静。义无不由之谓也。心包性。性具理。
前章只说性善。以著其本然之理已然之故。后章始说降才不殊。以破公都子三说之非。若知性善而才不殊。则天下古今贤愚之性一也。于此三说。不攻而自破。譬如人有表证三四之病。而良医治其内。则三四表证。一时快袪。
人之有欲。如木之有虫。虫蚀木心则其木死。欲蔽人心则其人恶。孟子所谓夜气之存者。即存心之谓也。其心存。则其气也无閒于昼夜。而常清明矣。不必向夜中操存。无时不操存。不必向朝前体验。无时不体验。
心有出入。岂谓一物在内。一物出外哉。以神明不测之妙。其出其入。无有定时。或如鸢而戾天。或如鱼而潜渊。燕越如咫尺。古今如瞬目。此所以操然后存。所以存之者。惟诚是已。所以诚之者。惟敬是已。敬亦非诚不做。陆棠持敬不诚。故归于不善。
夜气。即一未发境界。方其夜色向深。万籁俱寂之时。清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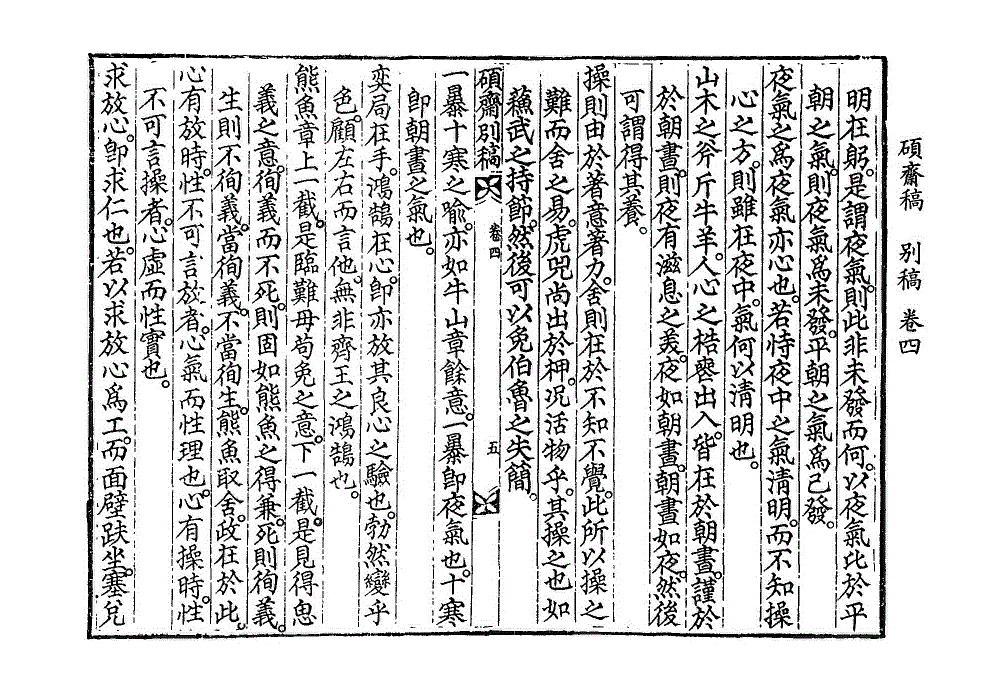 明在躬。是谓夜气。则此非未发而何。以夜气比于平朝之气。则夜气为未发。平朝之气为已发。
明在躬。是谓夜气。则此非未发而何。以夜气比于平朝之气。则夜气为未发。平朝之气为已发。夜气之为夜气亦心也。若恃夜中之气清明。而不知操心之方。则虽在夜中。气何以清明也。
山木之斧斤牛羊。人心之梏丧出入。皆在于朝昼。谨于于朝昼。则夜有滋息之美。夜如朝昼。朝昼如夜。然后可谓得其养。
操则由于著意著力。舍则在于不知不觉。此所以操之难而舍之易。虎兕尚出于柙。况活物乎。其操之也如苏武之持节。然后可以免伯鲁之失简。
一㬥十寒之喻。亦如牛山章馀意。一㬥即夜气也。十寒即朝昼之气也。
奕局在手。鸿鹄在心。即亦放其良心之验也。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无非齐王之鸿鹄也。
熊鱼章上一截。是临难毋苟免之意。下一截。是见得思义之意。徇义而不死。则固如熊鱼之得兼。死则徇义。生则不徇义。当徇义。不当徇生。熊鱼取舍。政在于此。
心有放时。性不可言放者。心气而性理也。心有操时。性不可言操者。心虚而性实也。
求放心。即求仁也。若以求放心为工。而面壁趺坐。塞兑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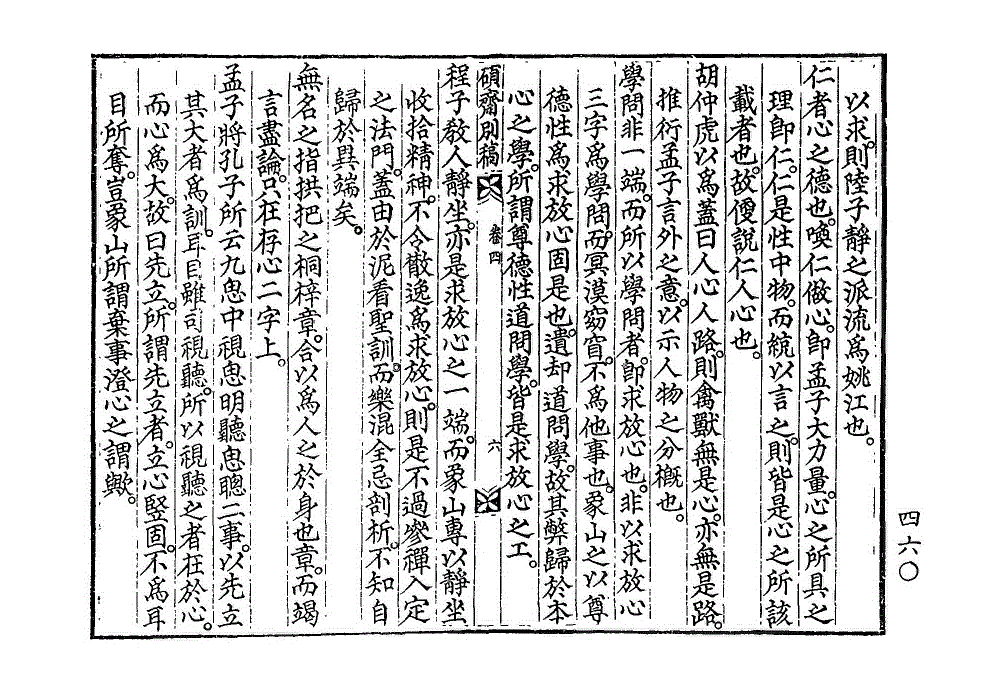 以求。则陆子静之派流为姚江也。
以求。则陆子静之派流为姚江也。仁者心之德也。唤仁做心。即孟子大力量。心之所具之理即仁。仁是性中物。而统以言之。则皆是心之所该载者也。故便说仁人心也。
胡仲虎以为盖曰人心人路。则禽兽无是心。亦无是路。推衍孟子言外之意。以示人物之分概也。
学问非一端。而所以学问者。即求放心也。非以求放心三字为学问。而冥漠窈窅。不为他事也。象山之以尊德性为求放心固是也。遗却道问学。故其弊归于本心之学。所谓尊德性道问学。皆是求放心之工。
程子教人静坐。亦是求放心之一端。而象山专以静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为求放心。则是不过参禅入定之法门。盖由于泥看圣训。而乐混全忌剖析。不知自归于异端矣。
无名之指拱把之桐梓章。合以为人之于身也章。而竭言尽论。只在存心二字上。
孟子将孔子所云九思中视思明听思聪二事。以先立其大者为训。耳目虽司视听。所以视听之者在于心。而心为大。故曰先立。所谓先立者。立心竖固。不为耳目所夺。岂象山所谓弃事澄心之谓欤。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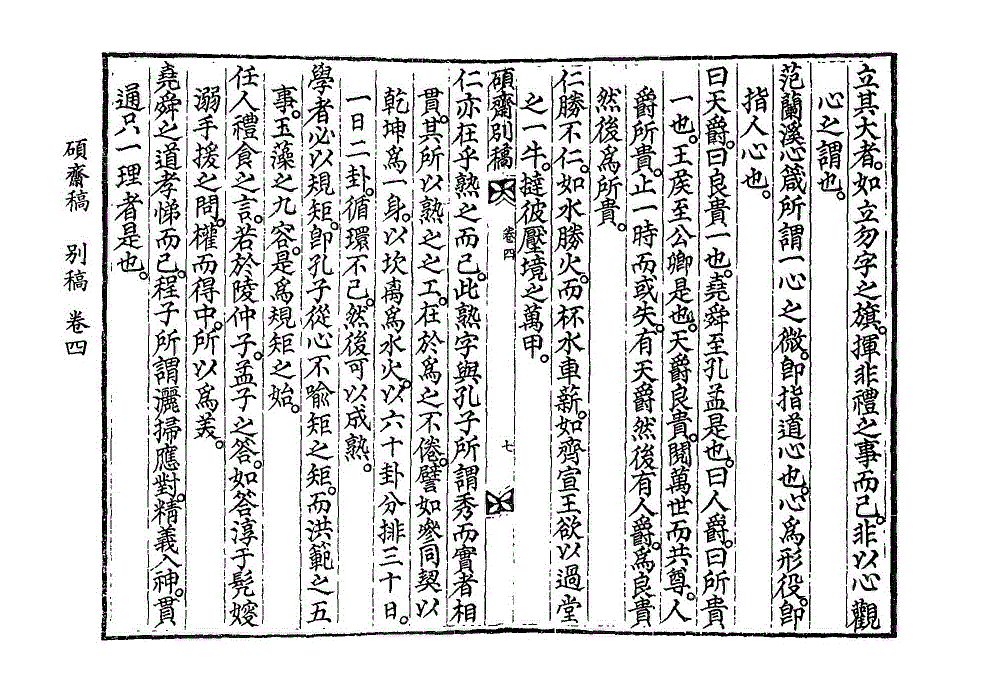 立其大者。如立勿字之旗。挥非礼之事而已。非以心观心之谓也。
立其大者。如立勿字之旗。挥非礼之事而已。非以心观心之谓也。范兰溪心箴所谓一心之微。即指道心也。心为形役。即指人心也。
曰天爵。曰良贵一也。尧舜至孔孟是也。曰人爵。曰所贵一也。王侯至公卿是也。天爵良贵。阅万世而共尊。人爵所贵。止一时而或失。有天爵然后有人爵。为良贵然后为所贵。
仁胜不仁。如水胜火。而杯水车薪。如齐宣王欲以过堂之一牛。挞彼压境之万甲。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熟字与孔子所谓秀而实者相贯。其所以熟之之工。在于为之不倦。譬如参同契以乾坤为一身。以坎离为水火。以六十卦分排三十日。一日二卦。循环不已。然后可以成熟。
学者必以规矩。即孔子从心不喻矩之矩。而洪范之五事。玉藻之九容。是为规矩之始。
任人礼食之言。若于陵仲子。孟子之答。如答淳于髡嫂溺手援之问。权而得中。所以为美。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程子所谓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者是也。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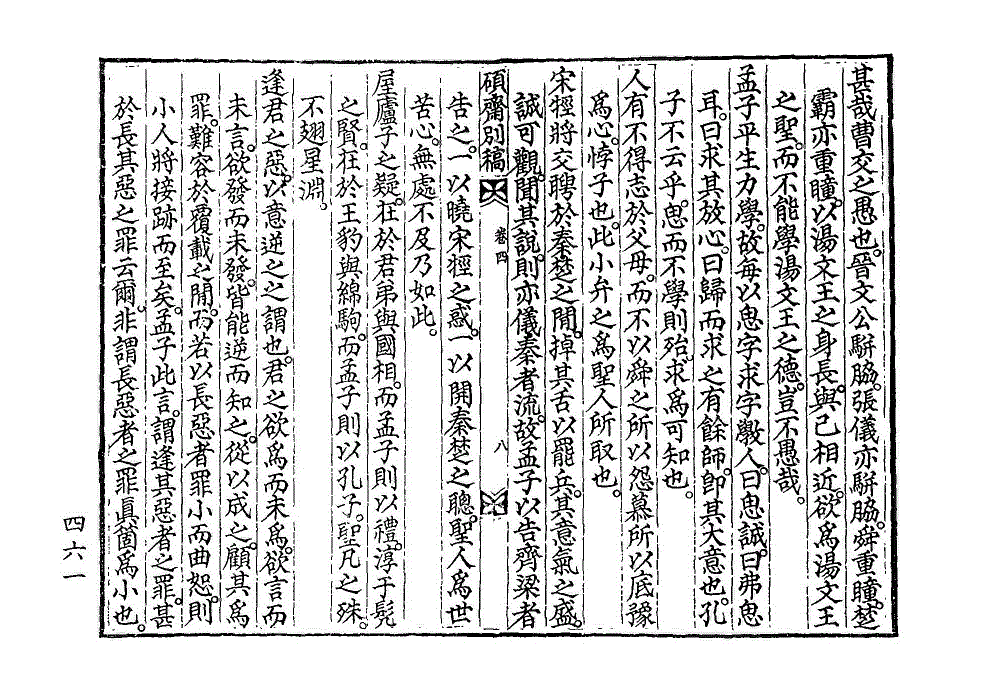 甚哉曹交之愚也。晋文公骈胁。张仪亦骈胁。舜重瞳。楚霸亦重瞳。以汤文王之身长。与己相近。欲为汤文王之圣。而不能学汤文王之德。岂不愚哉。
甚哉曹交之愚也。晋文公骈胁。张仪亦骈胁。舜重瞳。楚霸亦重瞳。以汤文王之身长。与己相近。欲为汤文王之圣。而不能学汤文王之德。岂不愚哉。孟子平生力学。故每以思字求字敩人。曰思诚。曰弗思耳。曰求其放心。曰归而求之有馀师。即其大意也。孔子不云乎。思而不学则殆。求为可知也。
人有不得志于父母。而不以舜之所以怨慕所以底豫为心。悖子也。此小弁之为圣人所取也。
宋牼将交聘于秦,楚之閒。掉其舌以罢兵。其意气之盛。诚可观。闻其说。则亦仪,秦者流。故孟子以告齐梁者告之。一以晓宋牼之惑。一以开秦楚之聪。圣人为世苦心。无处不及乃如此。
屋庐子之疑。在于君弟与国相。而孟子则以礼。淳于髡之贤。在于王豹与绵驹。而孟子则以孔子。圣凡之殊。不翅星渊。
逢君之恶。以意逆之之谓也。君之欲为而未为。欲言而未言。欲发而未发。皆能逆而知之。从以成之。顾其为罪。难容于覆载之閒。而若以长恶者罪小而曲恕。则小人将接迹而至矣。孟子此言。谓逢其恶者之罪。甚于长其恶之罪云尔。非谓长恶者之罪真个为小也。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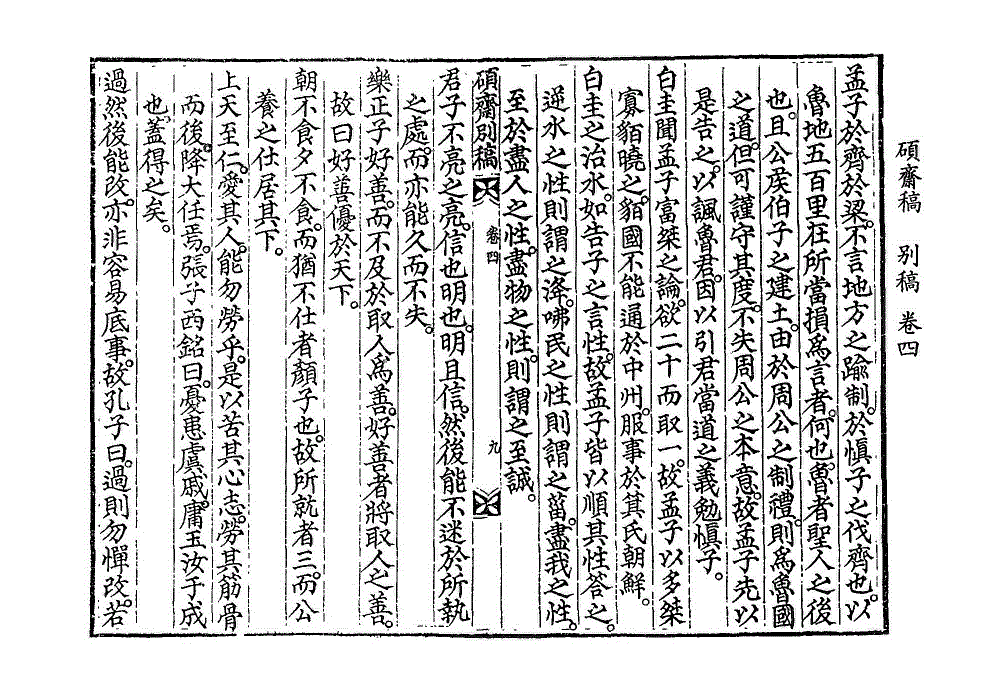 孟子于齐于梁。不言地方之踰制。于慎子之伐齐也。以鲁地五百里在所当损为言者。何也。鲁者圣人之后也。且公侯伯子之建土。由于周公之制礼。则为鲁国之道。但可谨守其度。不失周公之本意。故孟子先以是告之。以讽鲁君。因以引君当道之义勉慎子。
孟子于齐于梁。不言地方之踰制。于慎子之伐齐也。以鲁地五百里在所当损为言者。何也。鲁者圣人之后也。且公侯伯子之建土。由于周公之制礼。则为鲁国之道。但可谨守其度。不失周公之本意。故孟子先以是告之。以讽鲁君。因以引君当道之义勉慎子。白圭闻孟子富桀之论。欲二十而取一。故孟子以多桀寡貊晓之。貊国不能通于中州。服事于箕氏朝鲜。
白圭之治水。如告子之言性。故孟子皆以顺其性答之。逆水之性则谓之洚。咈民之性则谓之菑。尽我之性。至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谓之至诚。
君子不亮之亮。信也明也。明且信。然后能不迷于所执之处。而亦能久而不失。
乐正子好善。而不及于取人为善。好善者将取人之善。故曰好善优于天下。
朝不食夕不食。而犹不仕者颜子也。故所就者三。而公养之仕居其下。
上天至仁。爱其人。能勿劳乎。是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后。降大任焉。张子西铭曰。忧患虞戚。庸玉汝于成也。盖得之矣。
过然后能改。亦非容易底事。故孔子曰。过则勿惮改。若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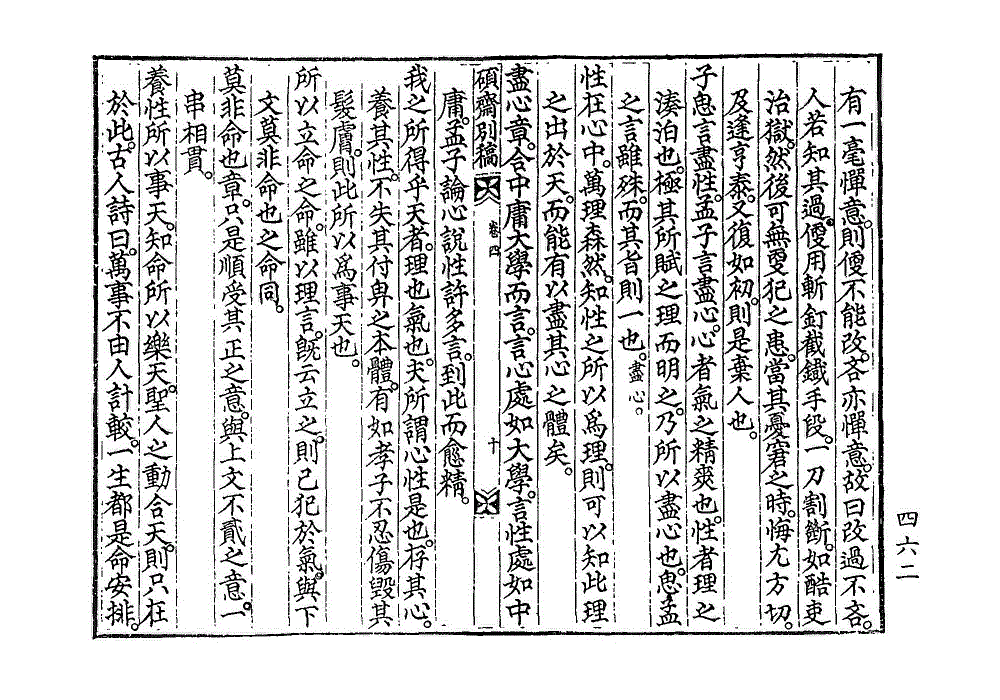 有一毫惮意。则便不能改。吝亦惮意。故曰改过不吝。人若知其过。便用斩钉截铁手段。一刀割断。如酷吏治狱。然后可无更犯之患。当其忧窘之时。悔尤方切。及逢亨泰。又复如初。则是弃人也。
有一毫惮意。则便不能改。吝亦惮意。故曰改过不吝。人若知其过。便用斩钉截铁手段。一刀割断。如酷吏治狱。然后可无更犯之患。当其忧窘之时。悔尤方切。及逢亨泰。又复如初。则是弃人也。子思言尽性。孟子言尽心。心者气之精爽也。性者理之凑泊也。极其所赋之理而明之。乃所以尽心也。思,孟之言虽殊。而其旨则一也。(尽心。)
性在心中。万理森然。知性之所以为理。则可以知此理之出于天。而能有以尽其心之体矣。
尽心章。合中庸大学而言。言心处如大学。言性处如中庸。孟子论心说性许多言。到此而愈精。
我之所得乎天者。理也气也。夫所谓心性是也。存其心。养其性。不失其付畀之本体。有如孝子不忍伤毁其发肤。则此所以为事天也。
所以立命之命。虽以理言。既云立之。则已犯于气。与下文莫非命也之命同。
莫非命也章。只是顺受其正之意。与上文不贰之意。一串相贯。
养性所以事天。知命所以乐天。圣人之动合天。则只在于此。古人诗曰。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3H 页
 其知道者之言乎。
其知道者之言乎。求在人者。固有不得之时。求在我者。岂无自得之喜。不患不得。患不求。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至则曰义曰礼曰智。如拔茅而连茹。以其汇进。
万物备于我。即本然之理。反身而诚。即实然之理也。强恕而行。即当然之工夫也。反而诚者。明而诚者也。恕而行者。致曲者也。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充然粹然。与天地同流之意。若非圣人。不能知此境有此乐。孔子乐而忘忧。颜子不改其乐。皆是莫大之乐。
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由之而不知道。皆不能知穷格之工。而行欲居于知先。故有此三病。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此救疗之资。
人而无耻。则无不可为之事。而其始则为机变之巧所滋长。竟至于稽颡贼庭。失节狼狈。而亦不之恤焉。如欲有耻心。亦自弗欺二字做将去。
贤王忘势。文王之访太公也。贤士忘人之势。汲黯揖大将军也。
穷不失义者。如闵子骞辞费宰。达不离道者。如伊尹尧舜君民。可以当之。宋句践好事游说。只务其外。不知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3L 页
 嚣嚣自得之义。故孟子以此谕之。凡为士者。以此章存心服膺。则自可以免循名弃实之病。而亦当晓然于为己为人之别矣。
嚣嚣自得之义。故孟子以此谕之。凡为士者。以此章存心服膺。则自可以免循名弃实之病。而亦当晓然于为己为人之别矣。伯夷,太公。不待文王而兴者。如江汉汝坟之诗。因文王作成之功而感化者也。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则率多薰陶于鸢鱼之休矣。
孔子曰。富而无骄则易。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孔孟之言。似若不同。而孔子则以贫而无怨。对富而无骄。故谓富者比于贫者。无骄易于无怨之谓也。孟子单说富贵。故谓之远过人也。
佚道使民。即先之劳之之意也。生道杀民。即刑一人而百人劝之意也。
上天所存。即神也。故风雨之所鼓润。无不化成。圣人体天。有神妙不测之存主。而德化所及。自然感化。如仪封人见孔子。而能知为圣人。则此孔子所存之神。化于所过之封人也。
仁言。假仁者亦有之。仁闻。是文王之令闻也。无其实则无是闻。善政。如葵坛之命。而善教则司徒之五典是也。鲁之国用不足。而犹行彻法。则是谓善政。百姓足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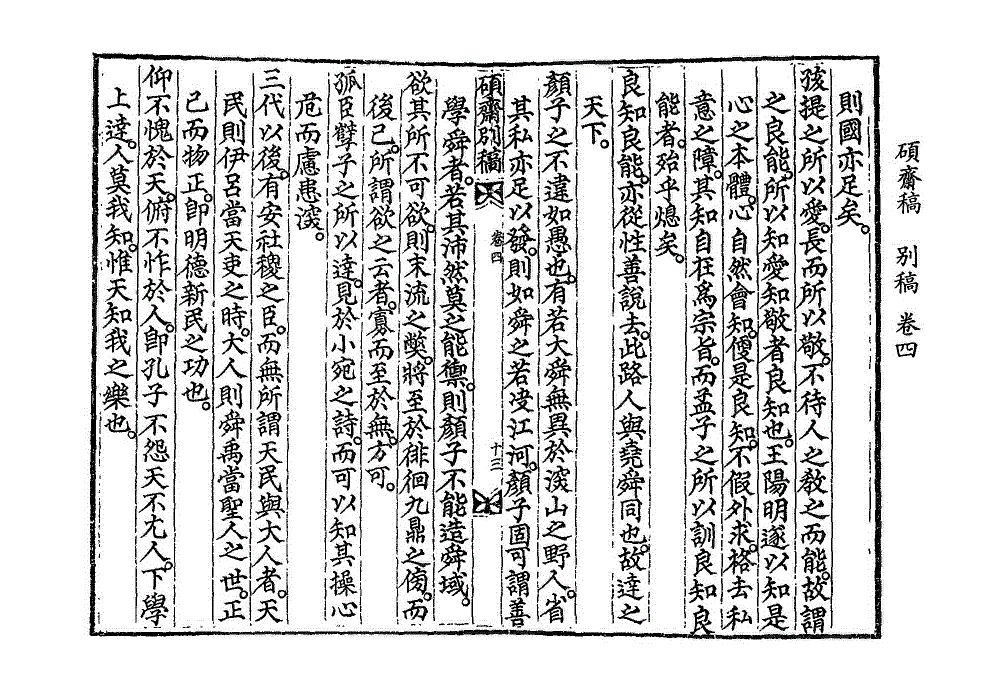 则国亦足矣。
则国亦足矣。孩提之所以爱。长而所以敬。不待人之教之而能。故谓之良能。所以知爱知敬者良知也。王阳明遂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格去私意之障。其知自在为宗旨。而孟子之所以训良知良能者。殆乎熄矣。
良知良能。亦从性善说去。此路人与尧舜同也。故达之天下。
颜子之不违如愚也。有若大舜无异于深山之野人。省其私亦足以发。则如舜之若决江河。颜子固可谓善学舜者。若其沛然莫之能御。则颜子不能造舜域。
欲其所不可欲。则末流之弊。将至于徘徊九鼎之傍。而后已。所谓欲之云者。寡而至于无。方可。
孤臣孽子之所以达。见于小宛之诗。而可以知其操心危而虑患深。
三代以后。有安社稷之臣。而无所谓天民与大人者。天民则伊吕当天吏之时。大人则舜禹当圣人之世。正己而物正。即明德新民之功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人莫我知。惟天知我之乐也。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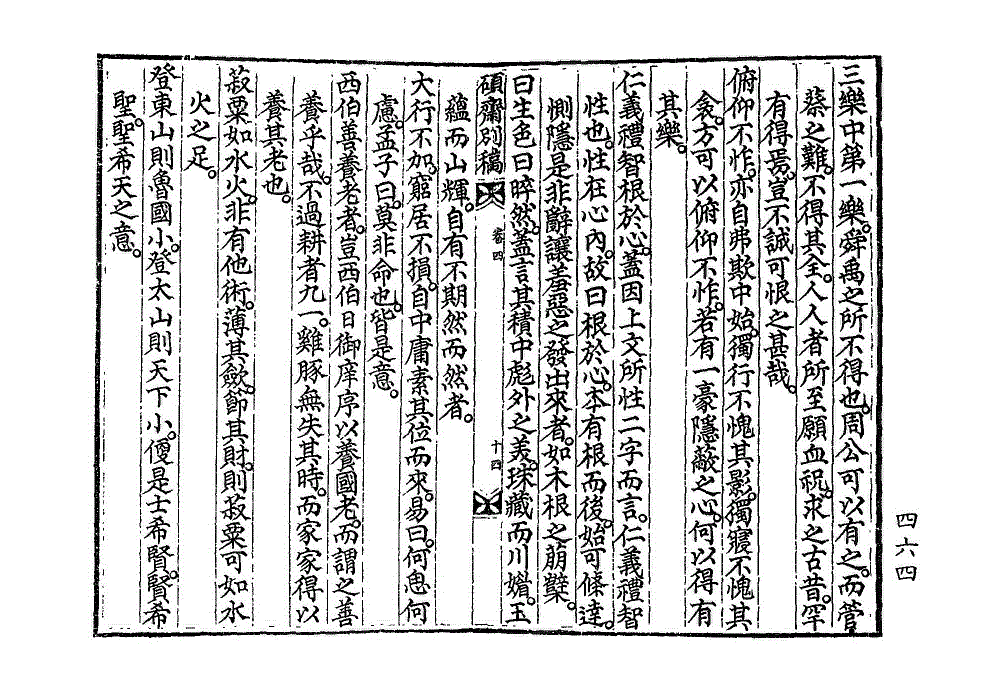 三乐中第一乐。舜禹之所不得也。周公可以有之。而管,蔡之难。不得其全。人人者所至愿血祝。求之古昔。罕有得焉。岂不诚可恨之甚哉。
三乐中第一乐。舜禹之所不得也。周公可以有之。而管,蔡之难。不得其全。人人者所至愿血祝。求之古昔。罕有得焉。岂不诚可恨之甚哉。俯仰不怍。亦自弗欺中始。独行不愧其影。独寝不愧其衾。方可以俯仰不怍。若有一豪隐蔽之心。何以得有其乐。
仁义礼智根于心。盖因上文所性二字而言。仁义礼智性也。性在心内。故曰根于心。本有根而后。始可条达。恻隐是非辞让羞恶之发出来者。如木根之萌蘖。
曰生色曰晬然。盖言其积中彪外之美。珠藏而川媚。玉蕴而山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自中庸素其位而来。易曰。何思何虑。孟子曰。莫非命也。皆是意。
西伯善养老者。岂西伯日御庠序以养国老。而谓之善养乎哉。不过耕者九一。鸡豚无失其时。而家家得以养其老也。
菽粟如水火。非有他术。薄其敛。节其财。则菽粟可如水火之足。
登东山则鲁国小。登太山则天下小。便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意。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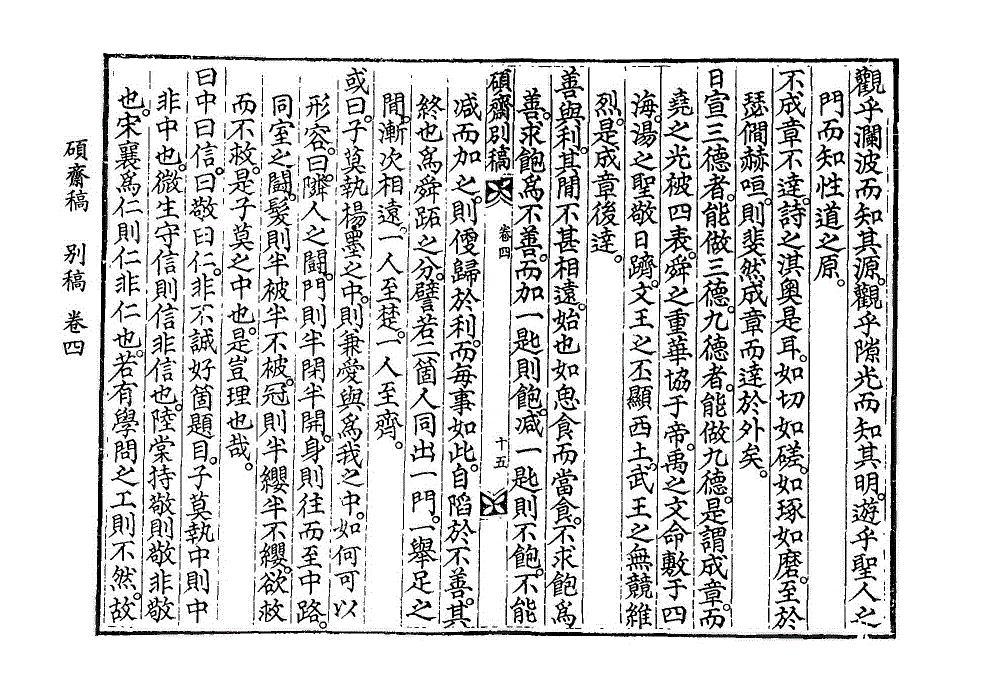 观乎澜波而知其源。观乎隙光而知其明。游乎圣人之门而知性道之原。
观乎澜波而知其源。观乎隙光而知其明。游乎圣人之门而知性道之原。不成章不达。诗之淇奥是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至于瑟僩赫咺。则斐然成章而达于外矣。
日宣三德者。能做三德。九德者。能做九德。是谓成章。而尧之光被四表。舜之重华协于帝。禹之文命敷于四海。汤之圣敬日跻。文王之丕显西土。武王之无竞维烈。是成章后达。
善与利。其閒不甚相远。始也如思食而当食。不求饱为善。求饱为不善。而加一匙则饱。减一匙则不饱。不能减而加之。则便归于利。而每事如此。自陷于不善。其终也为舜蹠之分。譬若二个人同出一门。一举足之閒。渐次相远。一人至楚。一人至齐。
或曰。子莫执杨,墨之中。则兼爱与为我之中。如何可以形容。曰。邻人之斗。门则半闭半开。身则往而至中路。同室之斗。发则半被半不被。冠则半缨半不缨。欲救而不救。是子莫之中也。是岂理也哉。
曰中曰信。曰敬曰仁。非不诚好个题目。子莫执中则中非中也。微生守信则信非信也。陆棠持敬则敬非敬也。宋襄为仁则仁非仁也。若有学问之工则不然。故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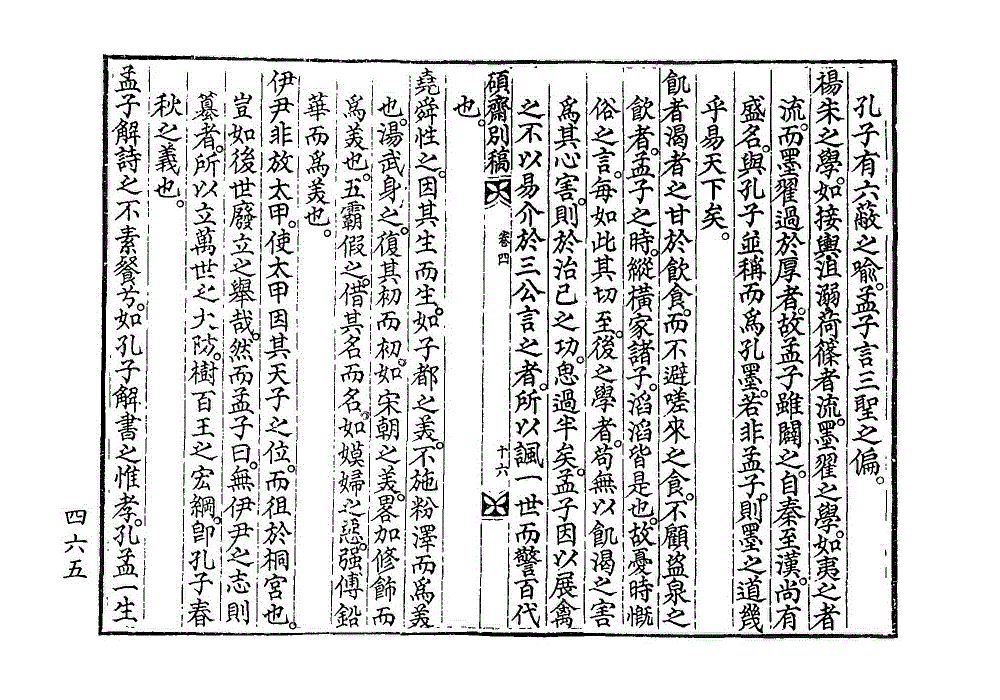 孔子有六蔽之喻。孟子言三圣之偏。
孔子有六蔽之喻。孟子言三圣之偏。杨朱之学。如接舆,沮溺,荷筱者流。墨翟之学。如夷之者流。而墨翟过于厚者。故孟子虽辟之。自秦至汉。尚有盛名。与孔子并称而为孔墨。若非孟子。则墨之道几乎易天下矣。
饥者渴者之甘于饮食。而不避嗟来之食。不顾盗泉之饮者。孟子之时。纵横家诸子。滔滔皆是也。故忧时慨俗之言。每如此其切至。后之学者。苟无以饥渴之害为其心害。则于治己之功。思过半矣。孟子因以展禽之不以易介于三公言之者。所以讽一世而警百代也。
尧舜性之。因其生而生。如子都之美。不施粉泽而为美也。汤武身之。复其初而初。如宋朝之美。略加修饰而为美也。五霸假之。借其名而名。如嫫妇之恶。强傅铅华而为美也。
伊尹非放太甲。使太甲因其天子之位。而徂于桐宫也。岂如后世废立之举哉。然而孟子曰。无伊尹之志则篡者。所以立万世之大防。树百王之宏纲。即孔子春秋之义也。
孟子解诗之不素餐兮。如孔子解书之惟孝。孔孟一生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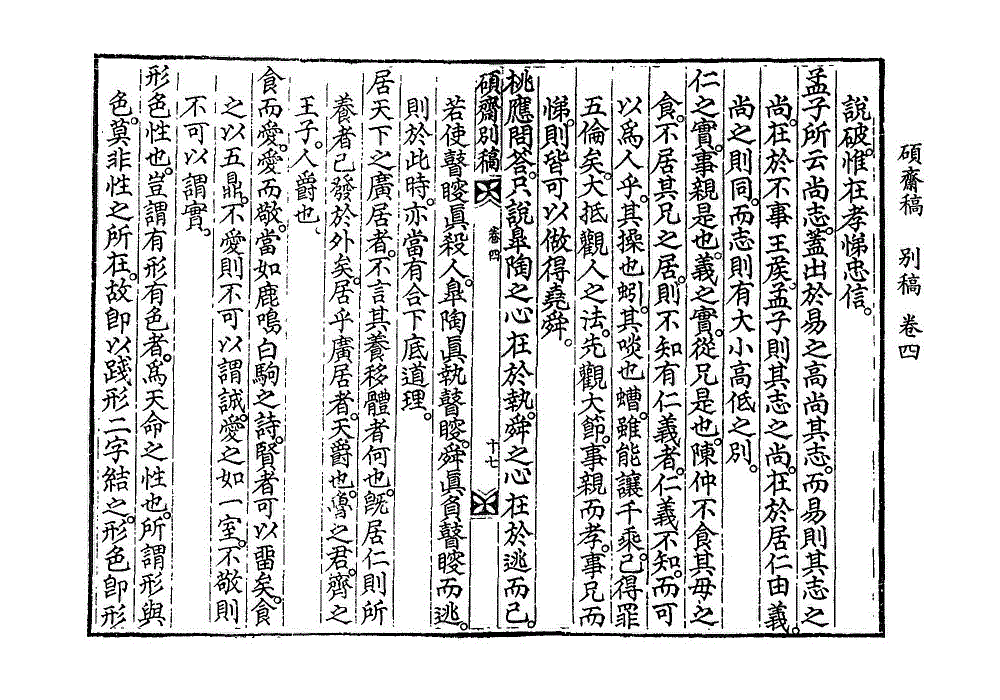 说破。惟在孝悌忠信。
说破。惟在孝悌忠信。孟子所云尚志。盖出于易之高尚其志。而易则其志之尚。在于不事王侯。孟子则其志之尚。在于居仁由义。尚之则同。而志则有大小高低之别。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陈仲不食其母之食。不居其兄之居。则不知有仁义者。仁义不知。而可以为人乎。其操也蚓。其啖也螬。虽能让千乘。已得罪五伦矣。大抵观人之法。先观大节。事亲而孝。事兄而悌。则皆可以做得尧舜。
桃应问答。只说皋陶之心在于执。舜之心在于逃而已。若使瞽瞍真杀人。皋陶真执瞽瞍。舜真负瞽瞍而逃。则于此时。亦当有合下底道理。
居天下之广居者。不言其养移体者何也。既居仁则所养者已发于外矣。居乎广居者。天爵也。鲁之君。齐之王子。人爵也。
食而爱。爱而敬。当如鹿鸣白驹之诗。贤者可以留矣。食之以五鼎。不爱则不可以谓诚。爱之如一室。不敬则不可以谓实。
形色性也。岂谓有形有色者。为天命之性也。所谓形与色。莫非性之所在。故即以践形二字结之。形色即形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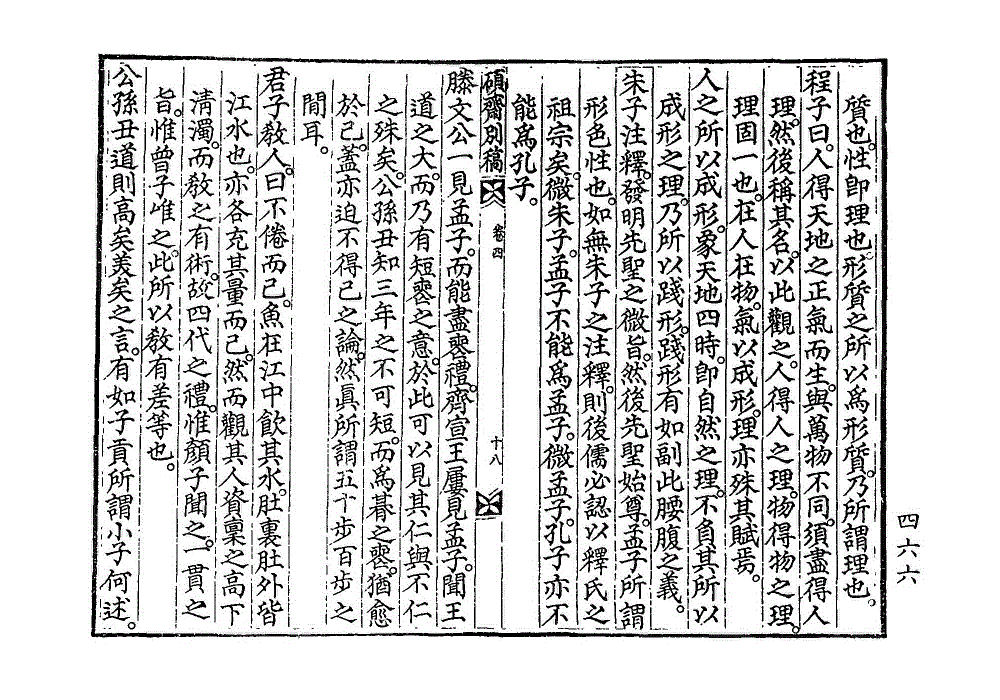 质也。性即理也。形质之所以为形质。乃所谓理也。
质也。性即理也。形质之所以为形质。乃所谓理也。程子曰。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须尽得人理。然后称其名。以此观之。人得人之理。物得物之理。理固一也。在人在物。气以成形。理亦殊其赋焉。
人之所以成形。象天地四时。即自然之理。不负其所以成形之理。乃所以践形。践形有如副此腰腹之义。
朱子注释。发明先圣之微旨。然后先圣始尊。孟子所谓形色性也。如无朱子之注释。则后儒必认以释氏之祖宗矣。微朱子。孟子不能为孟子。微孟子。孔子亦不能为孔子。
滕文公一见孟子。而能尽丧礼。齐宣王屡见孟子。闻王道之大。而乃有短丧之意。于此可以见其仁与不仁之殊矣。公孙丑知三年之不可短。而为期之丧。犹愈于己。盖亦迫不得已之论。然真所谓五十步百步之閒耳。
君子教人。曰不倦而已。鱼在江中饮其水。肚里肚外皆江水也。亦各充其量而已。然而观其人资禀之高下清浊。而教之有术。故四代之礼。惟颜子闻之。一贯之旨。惟曾子唯之。此所以教有差等也。
公孙丑道则高矣美矣之言。有如子贡所谓小子何述。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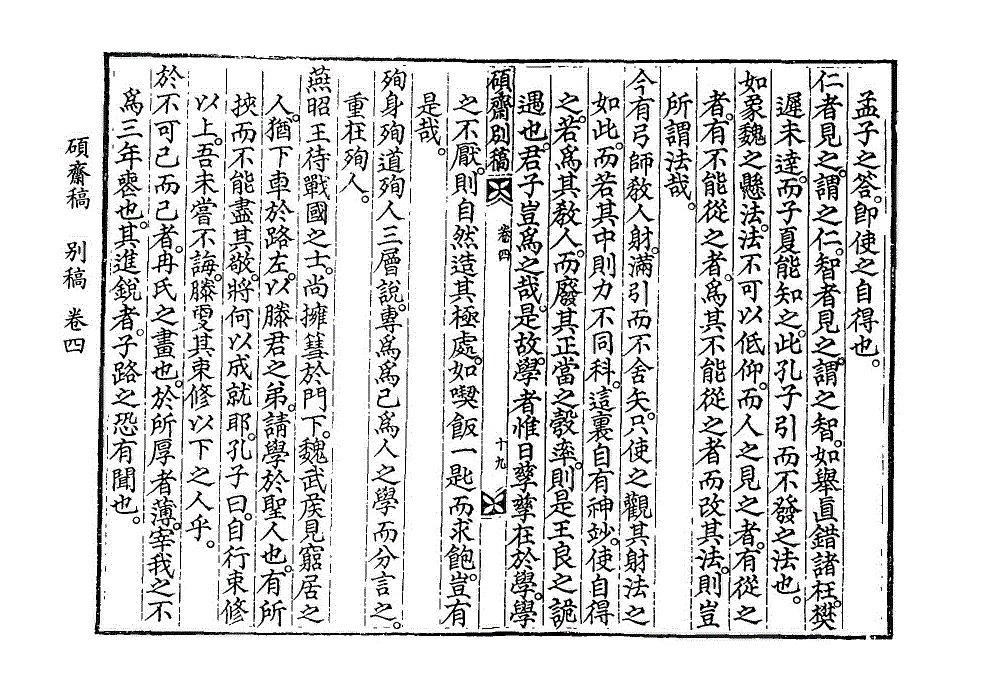 孟子之答。即使之自得也。
孟子之答。即使之自得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如举直错诸枉。樊迟未达。而子夏能知之。此孔子引而不发之法也。
如象魏之悬法。法不可以低仰。而人之见之者。有从之者。有不能从之者。为其不能从之者而改其法。则岂所谓法哉。
今有弓师教人射。满引而不舍矢。只使之观其射法之如此。而若其中则力不同科。这里自有神妙。使自得之。若为其教人。而废其正当之彀率。则是王良之诡遇也。君子岂为之哉。是故。学者惟日孳孳在于学。学之不厌。则自然造其极处。如吃饭一匙而求饱。岂有是哉。
殉身殉道殉人三层说。专为为己为人之学而分言之。重在殉人。
燕昭王待战国之士。尚拥彗于门下。魏武侯见穷居之人。犹下车于路左。以滕君之弟。请学于圣人也。有所挟而不能尽其敬。将何以成就耶。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不诲。滕更其束修以下之人乎。
于不可已而已者。冉氏之画也。于所厚者薄。宰我之不为三年丧也。其进锐者。子路之恐有闻也。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7L 页
 孟子七篇。都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曰申之以孝悌之义。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曰亲其亲。是亲亲也。曰制民产。曰保民而王。曰发政施仁。是仁民也。曰鸡彘不失其时。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是爱物也。
孟子七篇。都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曰申之以孝悌之义。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曰亲其亲。是亲亲也。曰制民产。曰保民而王。曰发政施仁。是仁民也。曰鸡彘不失其时。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是爱物也。知固周万物。而知所先务为真知。仁固施四海。而急于亲贤为大仁。故曾子曰知本。孔子曰汎爱众而亲仁。
春秋固无义战。比之六国。则差有胜焉。春秋之战。尚有退舍者矣。又有摄饮者矣。军容入于国容。杀戮无多。至六国之战。杀人盈野。水亦不流。生民之大祸。人世之极变。未有甚于此时也。故孟子以春秋与武成。历举以戒之。
曾子曰。战阵无勇。非孝也。孟子曰。善阵善战。大罪也。将于何从也。曾子所言者。如王者之师。顺时而动。人有从军而往者。若不勇往直前。杀身以成仁。则非所以显其亲之道也。孟子所言者。如列国之君。纵兵徇欲。朝攻而暮战。东败而西丧。生民涂炭。靡有了遗。而人有自称于君者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是导其君于率兽而食人也。故谓之大罪。大抵观书之法。当活不当泥。若如是也。王剪,白起。皆为孝子。太公,南仲。不免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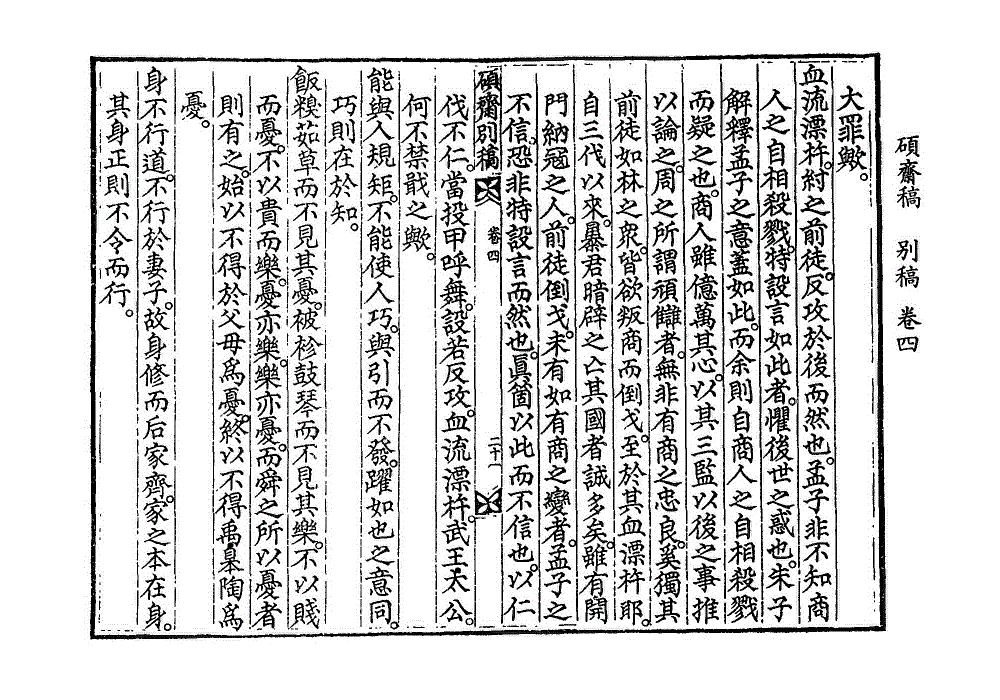 大罪欤。
大罪欤。血流漂杵。纣之前徒。反攻于后而然也。孟子非不知商人之自相杀戮。特设言如此者。惧后世之惑也。朱子解释孟子之意盖如此。而余则自商人之自相杀戮而疑之也。商人虽亿万其心。以其三监以后之事推以论之。周之所谓顽雠者。无非有商之忠良。奚独其前徒如林之众。皆欲叛商而倒戈。至于其血漂杵耶。自三代以来。㬥君暗辟之亡其国者诚多矣。虽有开门纳寇之人。前徒倒戈。未有如有商之变者。孟子之不信。恐非特设言而然也。真个以此而不信也。以仁伐不仁。当投甲呼舞。设若反攻。血流漂杵。武王,太公。何不禁戢之欤。
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与引而不发。跃如也之意同。巧则在于知。
饭糗茹草而不见其忧。被袗鼓琴而不见其乐。不以贱而忧。不以贵而乐。忧亦乐。乐亦忧。而舜之所以忧者则有之。始以不得于父母为忧。终以不得禹,𦤎陶为忧。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身修而后家齐。家之本在身。其身正则不令而行。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8L 页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以有得于心而不眩于事也。汉之卓茂。唐之狄仁杰。似乎近之。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以有得于心而不眩于事也。汉之卓茂。唐之狄仁杰。似乎近之。仁者人也。人之为人。即一仁字。充满一身都是仁。医家以手足痿痹为不仁。程子以为善者是也。
合而言之。道也。以礼义智信并言。然后尤为分明。尤延之所见高丽本。必是新罗金仁问,崔致远之徒。入唐游学从仕时。所购来者也。
貉稽不理于口。而孟子以文王孔子答之。盖其意若非文王孔子之圣。则于众口之憎。只可自修自省而已。及到圣人地位。则毁誉无足以动其心也。此为进稽之训也。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即器之反而求备之也。责人则明。恕己则昏。尤为在上者痼病。
径而不用则塞。井而不汲则眢。人之理义。在于扩充。而间断则庄周所谓蓬心是也。观于高子之为诗也尚声也。有欠于致知之工。可知已。
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佚。即人心也。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道。即道心也。先以人道统而言之。然后始可以言命之如此如彼。
自可欲之谓善。至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自有不易之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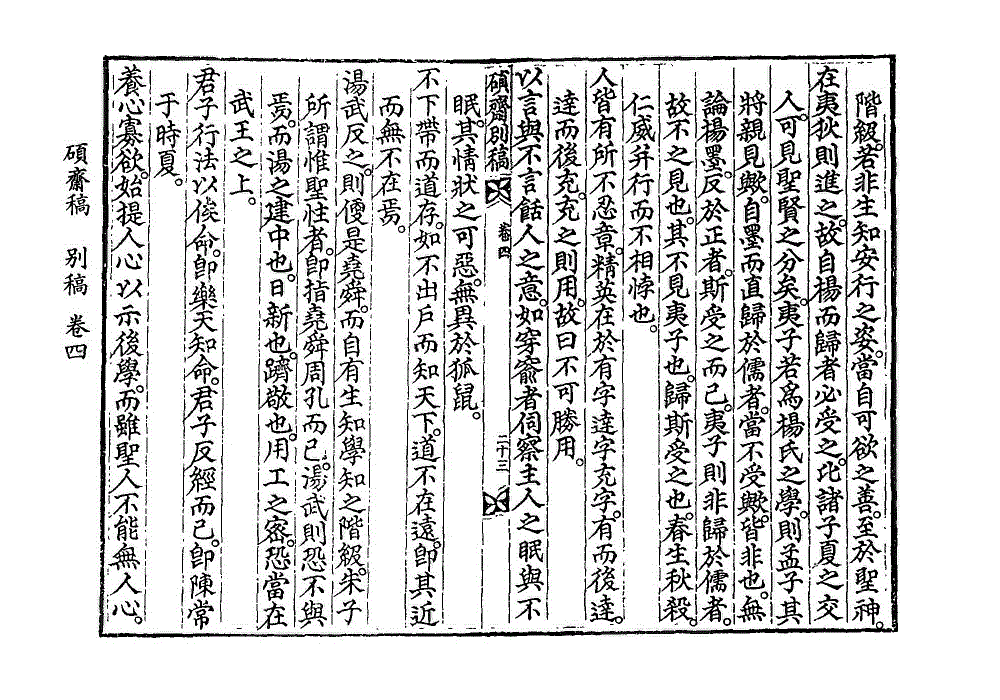 阶级。若非生知安行之姿。当自可欲之善。至于圣神。
阶级。若非生知安行之姿。当自可欲之善。至于圣神。在夷狄则进之。故自杨而归者必受之。比诸子夏之交人。可见圣贤之分矣。夷子若为杨氏之学。则孟子其将亲见欤。自墨而直归于儒者。当不受欤。皆非也。无论杨墨。反于正者。斯受之而已。夷子则非归于儒者。故不之见也。其不见夷子也。归斯受之也。春生秋杀。仁威并行而不相悖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精英在于有字达字充字。有而后达。达而后充。充之则用。故曰不可胜用。
以言与不言餂人之意。如穿窬者伺察主人之眠与不眠。其情状之可恶。无异于狐鼠。
不下带而道存。如不出户而知天下。道不在远。即其近而无不在焉。
汤武反之。则便是尧舜。而自有生知学知之阶级。朱子所谓惟圣性者。即指尧舜周孔而已。汤武则恐不与焉。而汤之建中也。日新也。跻敬也。用工之密。恐当在武王之上。
君子行法以俟命。即乐天知命。君子反经而已。即陈常于时夏。
养心寡欲。始提人心以示后学。而虽圣人不能无人心。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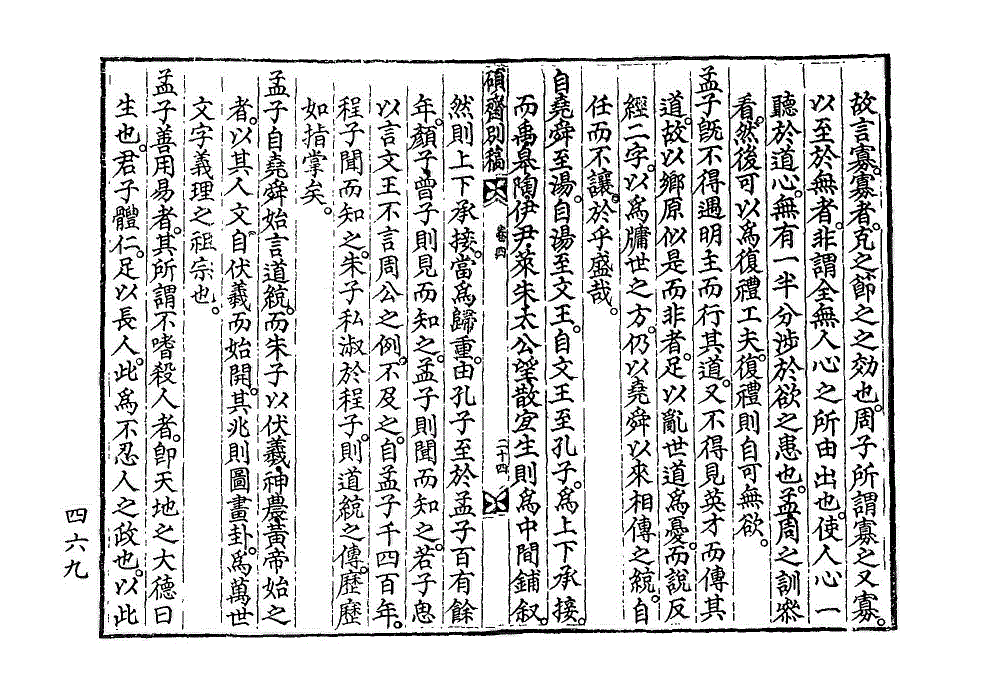 故言寡。寡者。克之节之之效也。周子所谓寡之又寡。以至于无者。非谓全无人心之所由出也。使人心一听于道心。无有一半分涉于欲之患也。孟,周之训参看。然后可以为复礼工夫。复礼则自可无欲。
故言寡。寡者。克之节之之效也。周子所谓寡之又寡。以至于无者。非谓全无人心之所由出也。使人心一听于道心。无有一半分涉于欲之患也。孟,周之训参看。然后可以为复礼工夫。复礼则自可无欲。孟子既不得遇明主而行其道。又不得见英才而传其道。故以乡原似是而非者。足以乱世道为忧。而说反经二字。以为牖世之方。仍以尧舜以来相传之统。自任而不让。于乎盛哉。
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王。自文王至孔子。为上下承接。而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则为中间铺叙。然则上下承接。当为归重。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馀年。颜子,曾子则见而知之。孟子则闻而知之。若子思以言文王不言周公之例。不及之。自孟子千四百年。程子闻而知之。朱子私淑于程子。则道统之传。历历如指掌矣。
孟子自尧舜始言道统。而朱子以伏羲,神农,黄帝始之者。以其人文。自伏羲而始开。其兆则图画卦。为万世文字义理之祖宗也。
孟子善用易者。其所谓不嗜杀人者。即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此为不忍人之政也。以此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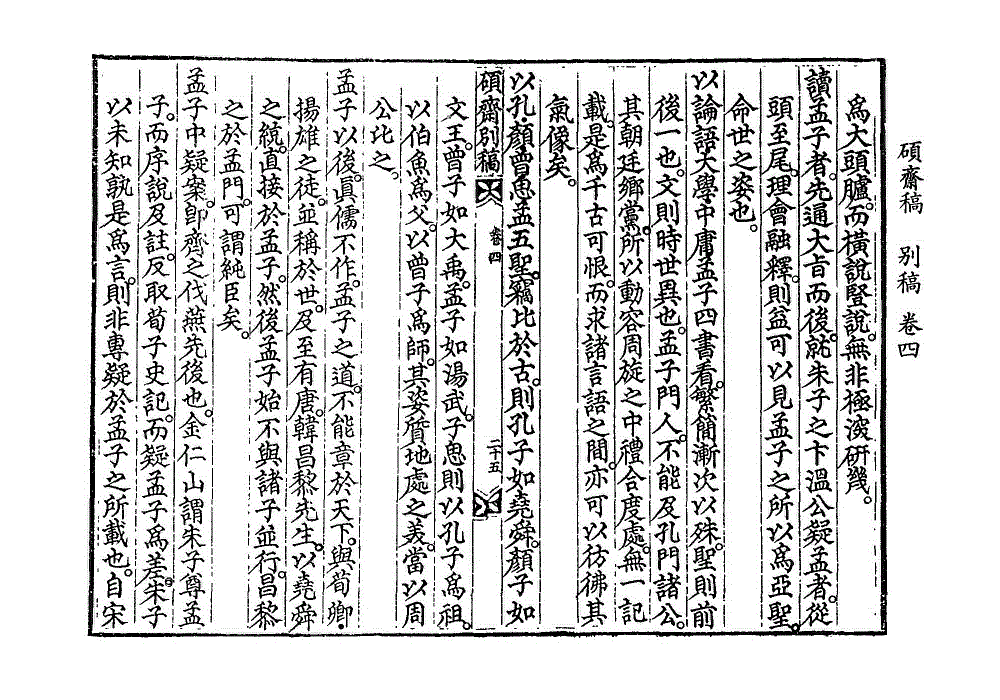 为大头胪。而横说竖说。无非极深研几。
为大头胪。而横说竖说。无非极深研几。读孟子者。先通大旨而后。就朱子之卞温公疑孟者。从头至尾。理会融释。则益可以见孟子之所以为亚圣。命世之姿也。
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看。繁简渐次以殊。圣则前后一也。文则时世异也。孟子门人。不能及孔门诸公。其朝廷乡党。所以动容周旋之中礼合度处。无一记载。是为千古可恨。而求诸言语之间。亦可以彷佛其气像矣。
以孔,颜,曾,思,孟五圣。窃比于古。则孔子如尧舜。颜子如文王。曾子如大禹。孟子如汤武。子思则以孔子为祖。以伯鱼为父。以曾子为师。其姿质地处之美。当以周公比之。
孟子以后。真儒不作。孟子之道。不能章于天下。与荀卿,扬雄之徒。并称于世。及至有唐。韩昌黎先生。以尧舜之统。直接于孟子。然后孟子始不与诸子并行。昌黎之于孟门。可谓纯臣矣。
孟子中疑案。即齐之伐燕先后也。金仁山谓朱子尊孟子。而序说及注。反取荀子史记。而疑孟子为差。朱子以未知孰是为言。则非专疑于孟子之所载也。自宋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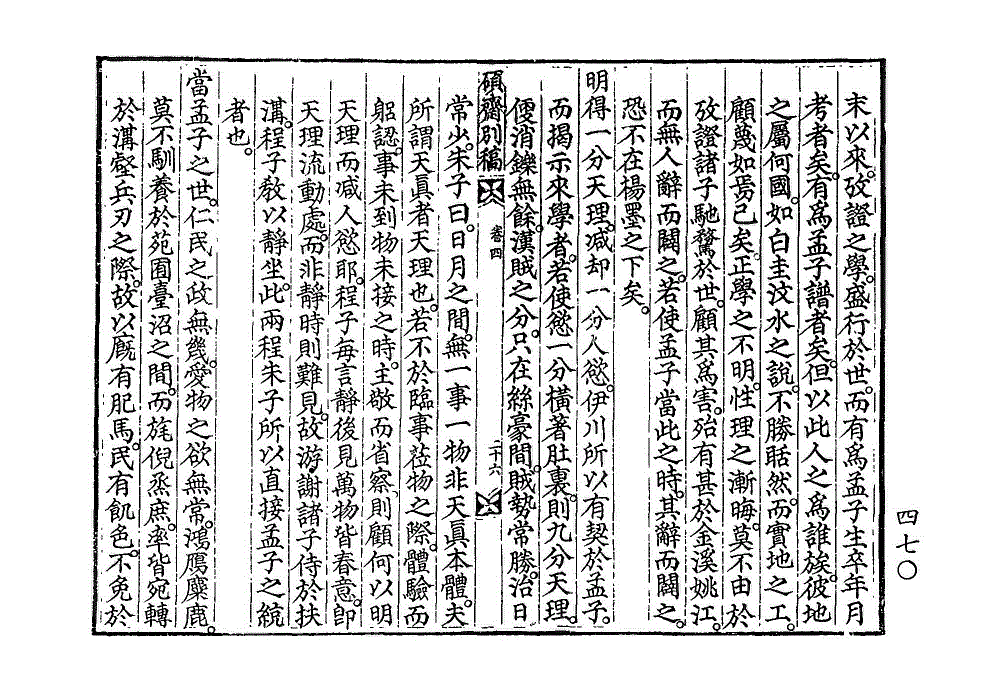 末以来。考證之学。盛行于世。而有为孟子生卒年月考者矣。有为孟子谱者矣。但以此人之为谁族。彼地之属何国。如白圭汶水之说。不胜聒然。而实地之工。顾蔑如焉已矣。正学之不明。性理之渐晦。莫不由于考證诸子驰骛于世。顾其为害。殆有甚于金溪姚江。而无人辞而辟之。若使孟子当此之时。其辞而辟之。恐不在杨墨之下矣。
末以来。考證之学。盛行于世。而有为孟子生卒年月考者矣。有为孟子谱者矣。但以此人之为谁族。彼地之属何国。如白圭汶水之说。不胜聒然。而实地之工。顾蔑如焉已矣。正学之不明。性理之渐晦。莫不由于考證诸子驰骛于世。顾其为害。殆有甚于金溪姚江。而无人辞而辟之。若使孟子当此之时。其辞而辟之。恐不在杨墨之下矣。明得一分天理。减却一分人欲。伊川所以有契于孟子。而揭示来学者。若使欲一分横著肚里。则九分天理。便消铄无馀。汉贼之分。只在丝豪间。贼势常胜。治日常少。朱子曰。日月之间。无一事一物非天真本体。夫所谓天真者天理也。若不于临事莅物之际。体验而躬认。事未到物未接之时。主敬而省察。则顾何以明天理而减人欲耶。程子每言静后见万物皆春意。即天理流动处。而非静时则难见。故游,谢诸子侍于扶沟。程子教以静坐。此两程朱子所以直接孟子之统者也。
当孟子之世。仁民之政无几。爱物之欲无常。鸿雁麋鹿。莫不驯养于苑囿台沼之间。而旄倪烝庶。率皆宛转于沟壑兵刃之际。故以厩有肥马。民有饥色。不免于
硕斋别稿卷之四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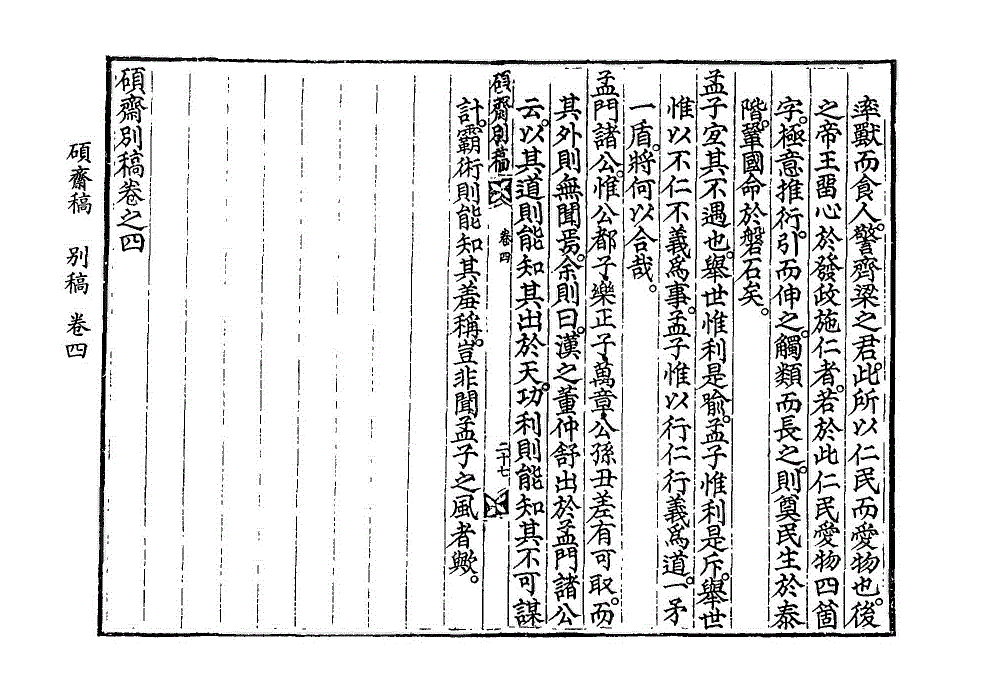 率兽而食人。警齐梁之君。此所以仁民而爱物也。后之帝王留心于发政施仁者。若于此仁民爱物四个字。极意推衍。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奠民生于泰阶。巩国命于磐石矣。
率兽而食人。警齐梁之君。此所以仁民而爱物也。后之帝王留心于发政施仁者。若于此仁民爱物四个字。极意推衍。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奠民生于泰阶。巩国命于磐石矣。孟子宜其不遇也。举世惟利是喻。孟子惟利是斥。举世惟以不仁不义为事。孟子惟以行仁行义为道。一矛一盾。将何以合哉。
孟门诸公。惟公都子,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差有可取。而其外则无闻焉。余则曰。汉之董仲舒出于孟门诸公云。以其道则能知其出于天。功利则能知其不可谋计。霸术则能知其羞称。岂非闻孟子之风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