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三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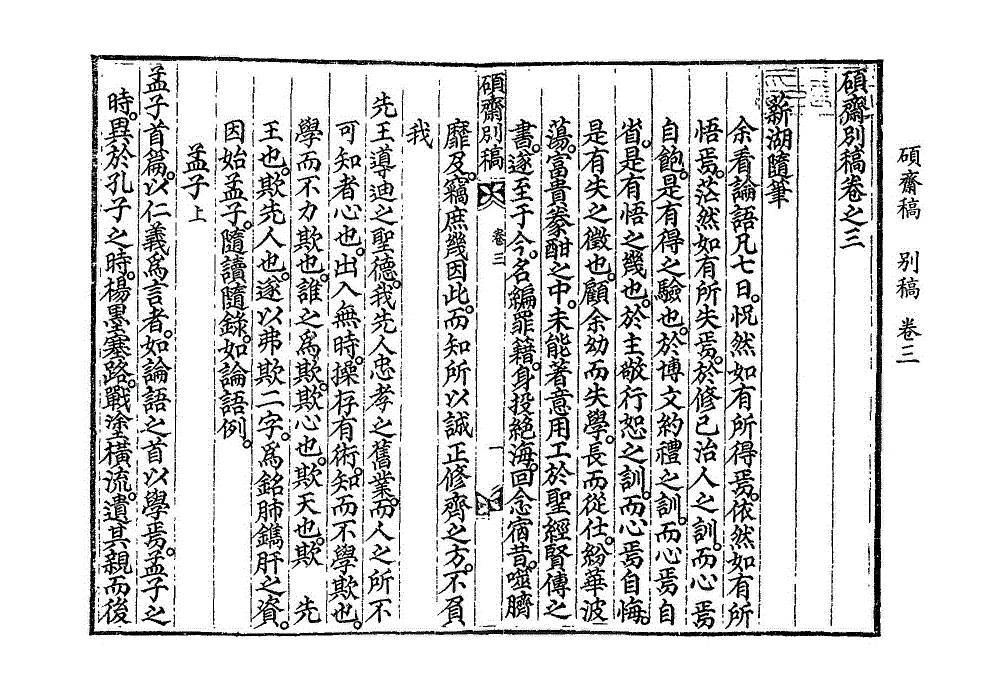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余看论语凡七日。恍然如有所得焉。依然如有所悟焉。茫然如有所失焉。于修己治人之训。而心焉自饱。是有得之验也。于博文约礼之训。而心焉自省。是有悟之几也。于主敬行恕之训。而心焉自悔。是有失之徵也。顾余幼而失学。长而从仕。纷华波荡。富贵豢酣之中。未能著意用工于圣经贤传之书。遂至于今。名编罪籍。身投绝海。回念宿昔。噬脐靡及。窃庶几因此。而知所以诚正修齐之方。不负我 先王导迪之圣德。我先人忠孝之旧业。而人之所不可知者心也。出入无时。操存有术。知而不学欺也。学而不力欺也。谁之为欺。欺心也。欺天也。欺 先王也。欺先人也。遂以弗欺二字。为铭肺镌肝之资。因始孟子。随读随录。如论语例。
孟子[上]
孟子首篇。以仁义为言者。如论语之首以学焉。孟子之时。异于孔子之时。杨墨塞路。战涂横流。遗其亲而后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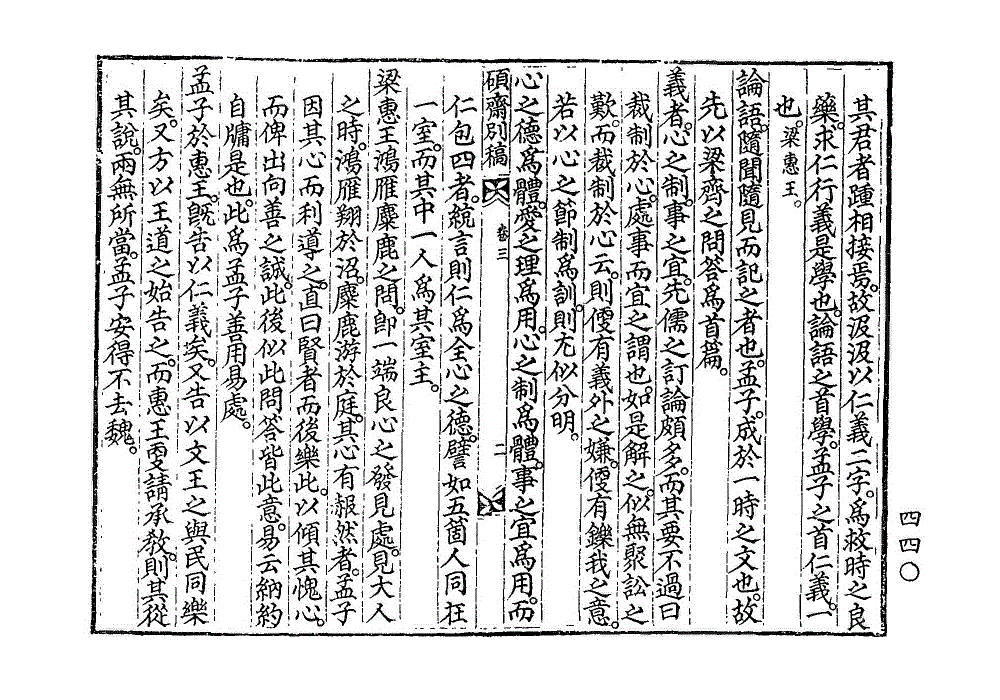 其君者踵相接焉。故汲汲以仁义二字。为救时之良药。求仁行义是学也。论语之首学。孟子之首仁义。一也。(梁惠王。)
其君者踵相接焉。故汲汲以仁义二字。为救时之良药。求仁行义是学也。论语之首学。孟子之首仁义。一也。(梁惠王。)论语。随闻随见而记之者也。孟子。成于一时之文也。故先以梁,齐之问答为首篇。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先儒之订论颇多。而其要不过曰裁制于心。处事而宜之谓也。如是解之。似无聚讼之叹。而裁制于心云。则便有义外之嫌。便有铄我之意。若以心之节制为训。则尤似分明。
心之德为体。爱之理为用。心之制为体。事之宜为用。而仁包四者。统言则仁为全心之德。譬如五个人同在一室。而其中一人为其室主。
梁惠王鸿雁麋鹿之问。即一端良心之发见处。见大人之时。鸿雁翔于沼。麋鹿游于庭。其心有赧然者。孟子因其心而利导之。直曰贤者而后乐此。以倾其愧心。而俾出向善之诚。此后似此问答皆此意。易云纳约自牖是也。此为孟子善用易处。
孟子于惠王。既告以仁义矣。又告以文王之与民同乐矣。又方以王道之始告之。而惠王更请承教。则其从其说。两无所当。孟子安得不去魏。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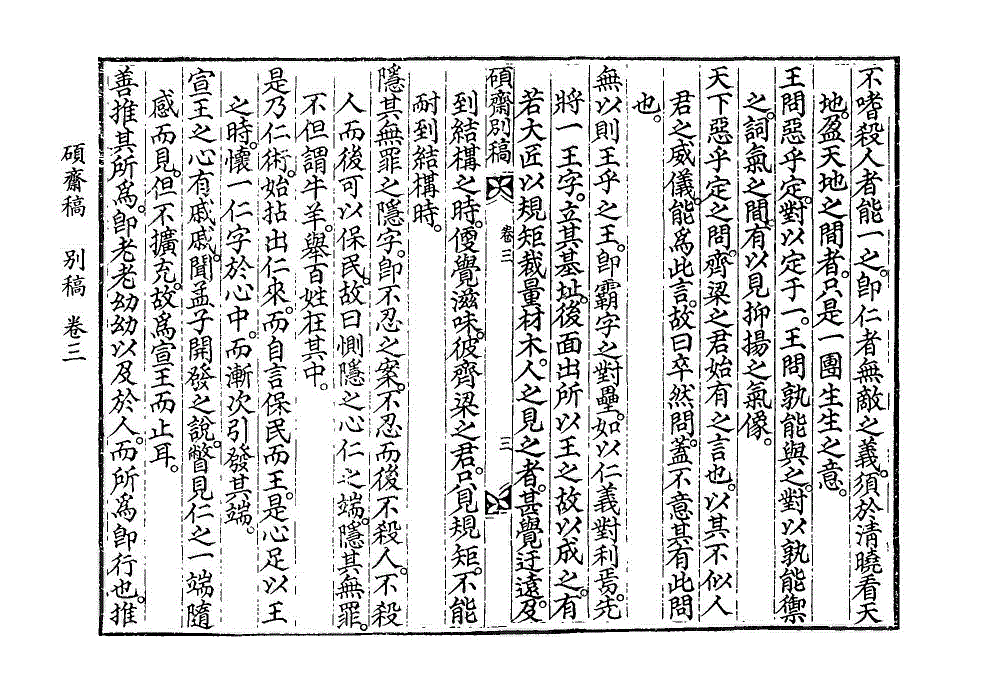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仁者无敌之义。须于清晓看天地。盈天地之间者。只是一团生生之意。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仁者无敌之义。须于清晓看天地。盈天地之间者。只是一团生生之意。王问恶乎定。对以定于一。王问孰能与之。对以孰能御之。词气之间。有以见抑扬之气像。
天下恶乎定之问。齐梁之君始有之言也。以其不似人君之威仪。能为此言。故曰卒然问。盖不意其有此问也。
无以则王乎之王。即霸字之对垒。如以仁义对利焉。先将一王字。立其基址。后面出所以王之故以成之。有若大匠以规矩裁量材木。人之见之者。甚觉迂远。及到结构之时。便觉滋味。彼齐梁之君。只见规矩。不能耐到结构时。
隐其无罪之隐字。即不忍之案。不忍而后不杀人。不杀人而后可以保民。故曰恻隐之心仁之端。隐其无罪。不但谓牛羊。举百姓在其中。
是乃仁术。始拈出仁来。而自言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之时。怀一仁字于心中。而渐次引发其端。
宣王之心有戚戚。闻孟子开发之说。瞥见仁之一端随感而见。但不扩充。故为宣王而止耳。
善推其所为。即老老幼幼以及于人。而所为即行也。推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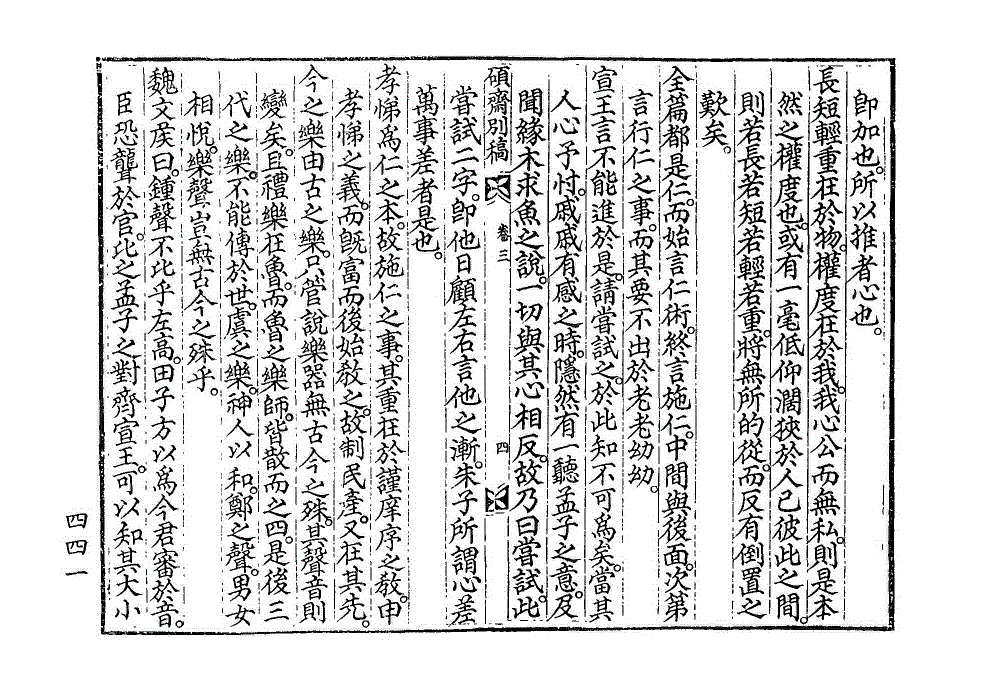 即加也。所以推者心也。
即加也。所以推者心也。长短轻重在于物。权度在于我。我心公而无私。则是本然之权度也。或有一毫低仰阔狭于人己彼此之间。则若长若短若轻若重。将无所的从。而反有倒置之叹矣。
全篇都是仁。而始言仁术。终言施仁。中间与后面。次第言行仁之事。而其要不出于老老幼幼。
宣王言不能进于是。请尝试之。于此知不可为矣。当其人心予忖。戚戚有感之时。隐然有一听孟子之意。及闻缘木求鱼之说。一切与其心相反。故乃曰尝试。此尝试二字。即他日顾左右言他之渐。朱子所谓心差万事差者是也。
孝悌为仁之本。故施仁之事。其重在于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而既富而后始教之。故制民产。又在其先。
今之乐由古之乐。只管说乐器无古今之殊。其声音则变矣。且礼乐在鲁。而鲁之乐师。皆散而之四。是后三代之乐。不能传于世。虞之乐。神人以和。郑之声。男女相悦。乐声岂无古今之殊乎。
魏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以为今君审于音。臣恐聋于官。比之孟子之对齐宣王。可以知其大小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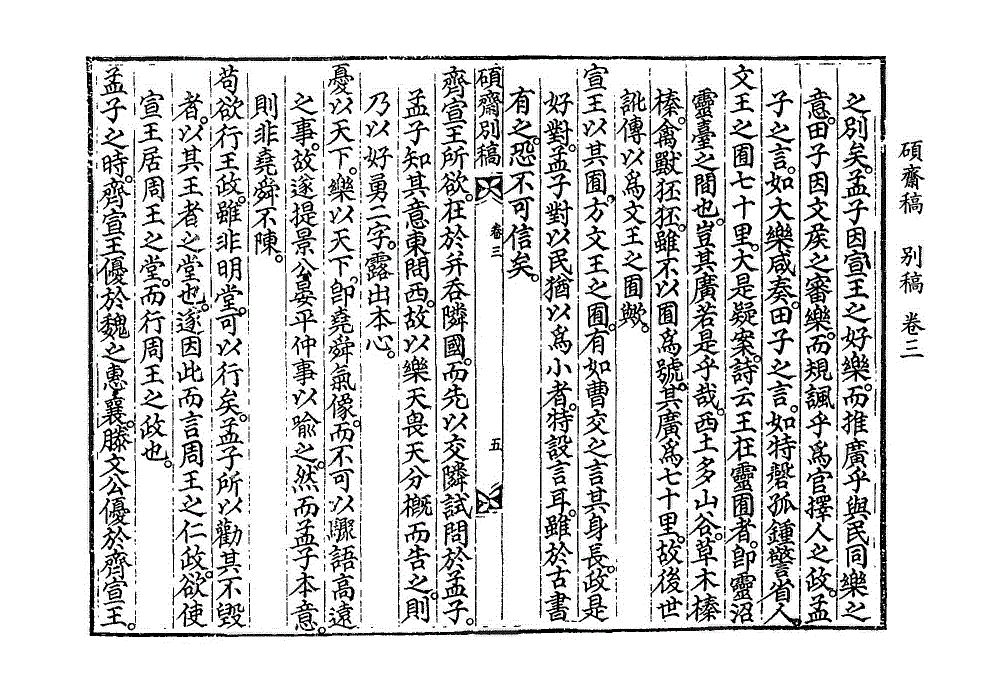 之别矣。孟子因宣王之好乐。而推广乎与民同乐之意。田子因文侯之审乐。而规讽乎为官择人之政。孟子之言。如大乐咸奏。田子之言。如特磬孤钟警省人。
之别矣。孟子因宣王之好乐。而推广乎与民同乐之意。田子因文侯之审乐。而规讽乎为官择人之政。孟子之言。如大乐咸奏。田子之言。如特磬孤钟警省人。文王之囿七十里。大是疑案。诗云王在灵囿者。即灵沼灵台之间也。岂其广若是乎哉。西土多山谷。草木榛榛。禽兽狉狉。虽不以囿为号。其广为七十里。故后世讹传以为文王之囿欤。
宣王以其囿。方文王之囿。有如曹交之言其身长。政是好对。孟子对以民犹以为小者。特设言耳。虽于古书有之。恐不可信矣。
齐宣王所欲。在于并吞邻国。而先以交邻试问于孟子。孟子知其意东问西。故以乐天畏天分概而告之。则乃以好勇二字。露出本心。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即尧舜气像。而不可以骤语高远之事。故遂提景公,晏平仲事以喻之。然而孟子本意。则非尧舜不陈。
苟欲行王政。虽非明堂。可以行矣。孟子所以劝其不毁者。以其王者之堂也。遂因此而言周王之仁政。欲使宣王居周王之堂。而行周王之政也。
孟子之时。齐宣王优于魏之惠,襄。滕文公优于齐宣王。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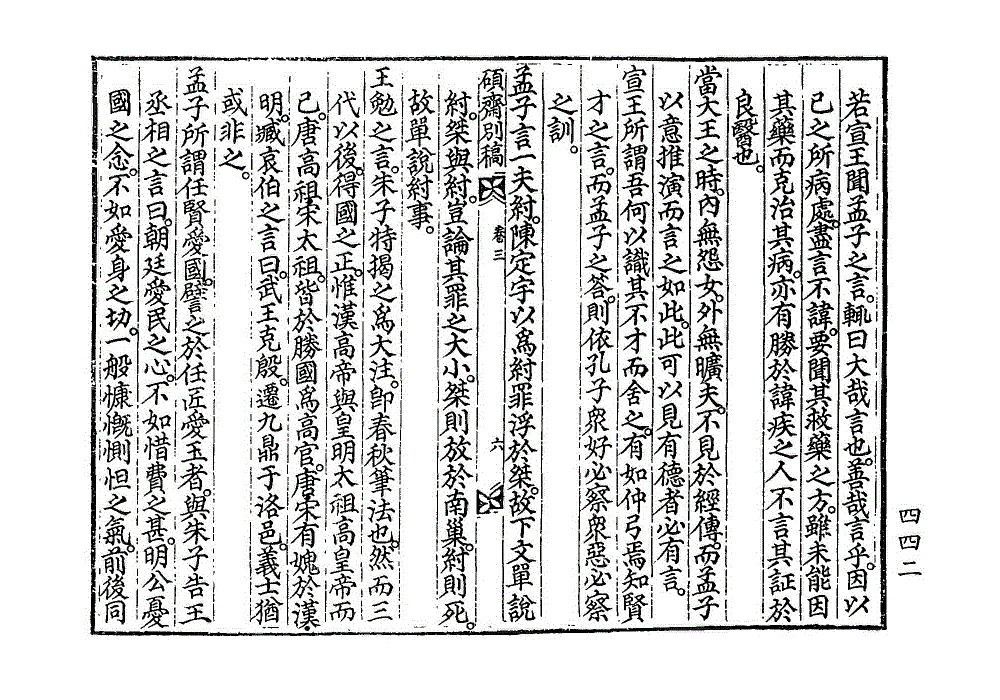 若宣王闻孟子之言。辄曰大哉言也。善哉言乎。因以己之所病处。尽言不讳。要闻其救药之方。虽未能因其药而克治其病。亦有胜于讳疾之人不言其证于良医也。
若宣王闻孟子之言。辄曰大哉言也。善哉言乎。因以己之所病处。尽言不讳。要闻其救药之方。虽未能因其药而克治其病。亦有胜于讳疾之人不言其证于良医也。当大王之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不见于经传。而孟子以意推演而言之如此。此可以见有德者必有言。
宣王所谓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有如仲弓焉知贤才之言。而孟子之答。则依孔子众好必察众恶必察之训。
孟子言一夫纣。陈定宇以为纣罪浮于桀。故下文单说纣。桀与纣。岂论其罪之大小。桀则放于南巢。纣则死。故单说纣事。
王勉之言。朱子特揭之为大注。即春秋笔法也。然而三代以后。得国之正。惟汉高帝与皇明太祖高皇帝而已。唐高祖,宋太祖。皆于胜国为高官。唐,宋有愧于汉,明。臧哀伯之言曰。武王克殷。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
孟子所谓任贤爱国。譬之于任匠爱玉者。与朱子告王丞相之言曰。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一般慷慨恻怛之气。前后同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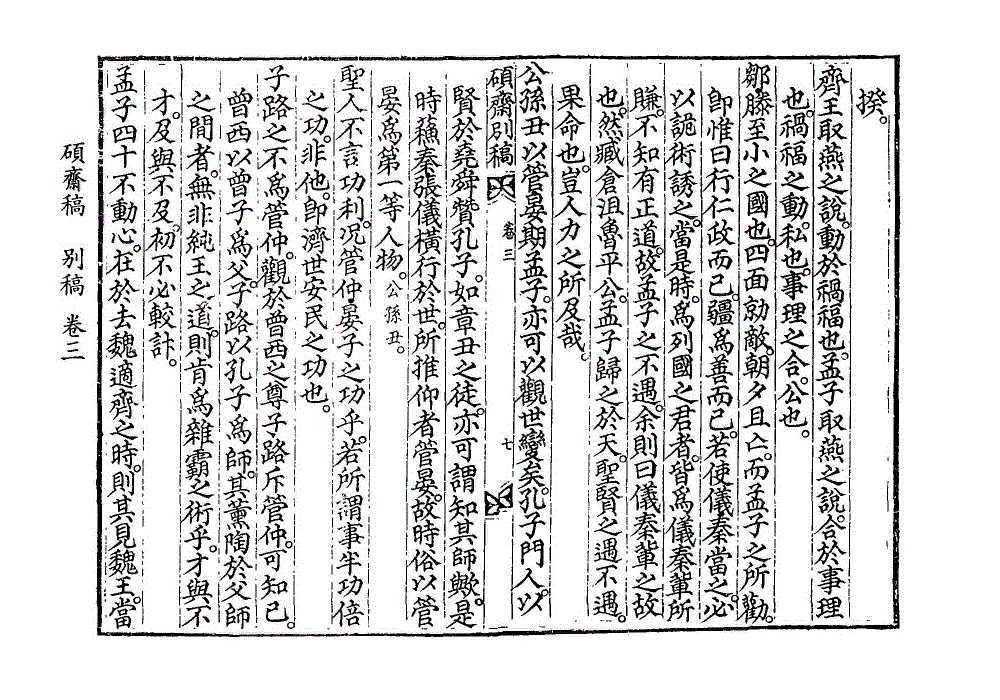 揆。
揆。齐王取燕之说。动于祸福也。孟子取燕之说。合于事理也。祸福之动。私也。事理之合。公也。
邹,滕至小之国也。四面勍敌。朝夕且亡。而孟子之所劝。即惟曰行仁政而已。疆为善而已。若使仪,秦当之。必以诡术诱之。当是时。为列国之君者。皆为仪秦辈所赚。不知有正道。故孟子之不遇。余则曰仪秦辈之故也。然臧仓沮鲁平公。孟子归之于天。圣贤之遇不遇。果命也。岂人力之所及哉。
公孙丑以管,晏期孟子。亦可以观世变矣。孔子门人。以贤于尧舜赞孔子。如章丑之徒。亦可谓知其师欤。是时苏秦,张仪横行于世。所推仰者管晏。故时俗以管晏为第一等人物。(公孙丑。)
圣人不言功利。况管仲,晏子之功乎。若所谓事半功倍之功。非他。即济世安民之功也。
子路之不为管仲。观于曾西之尊子路斥管仲。可知已。曾西以曾子为父。子路以孔子为师。其薰陶于父师之间者。无非纯王之道。则肯为杂霸之术乎。才与不才。及与不及。初不必较计。
孟子四十不动心。在于去魏适齐之时。则其见魏王。当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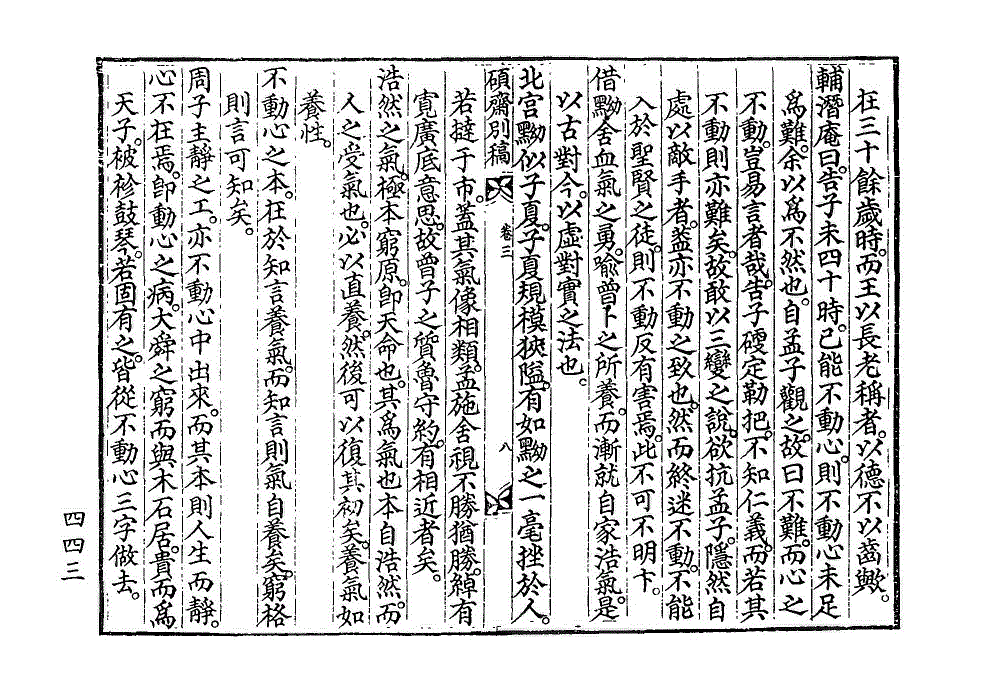 在三十馀岁时。而王以长老称者。以德不以齿欤。
在三十馀岁时。而王以长老称者。以德不以齿欤。辅潜庵曰。告子未四十时。已能不动心。则不动心未足为难。余以为不然也。自孟子观之。故曰不难。而心之不动。岂易言者哉。告子硬定勒把。不知仁义。而若其不动则亦难矣。故敢以三变之说。欲抗孟子。隐然自处以敌手者。盖亦不动之致也。然而终迷不动。不能入于圣贤之徒。则不动反有害焉。此不可不明卞。
借黝,舍血气之勇。喻曾,卜之所养。而渐就自家浩气。是以古对今。以虚对实之法也。
北宫黝似子夏。子夏规模狭隘。有如黝之一毫挫于人。若挞于市。盖其气像相类。孟施舍视不胜犹胜。绰有宽广底意思。故曾子之质鲁守约。有相近者矣。
浩然之气。极本穷原。即天命也。其为气也本自浩然。而人之受气也。必以直养。然后可以复其初矣。养气如养性。
不动心之本。在于知言养气。而知言则气自养矣。穷格则言可知矣。
周子主静之工。亦不动心中出来。而其本则人生而静。
心不在焉。即动心之病。大舜之穷而与木石居。贵而为天子。被袗鼓琴。若固有之。皆从不动心三字做去。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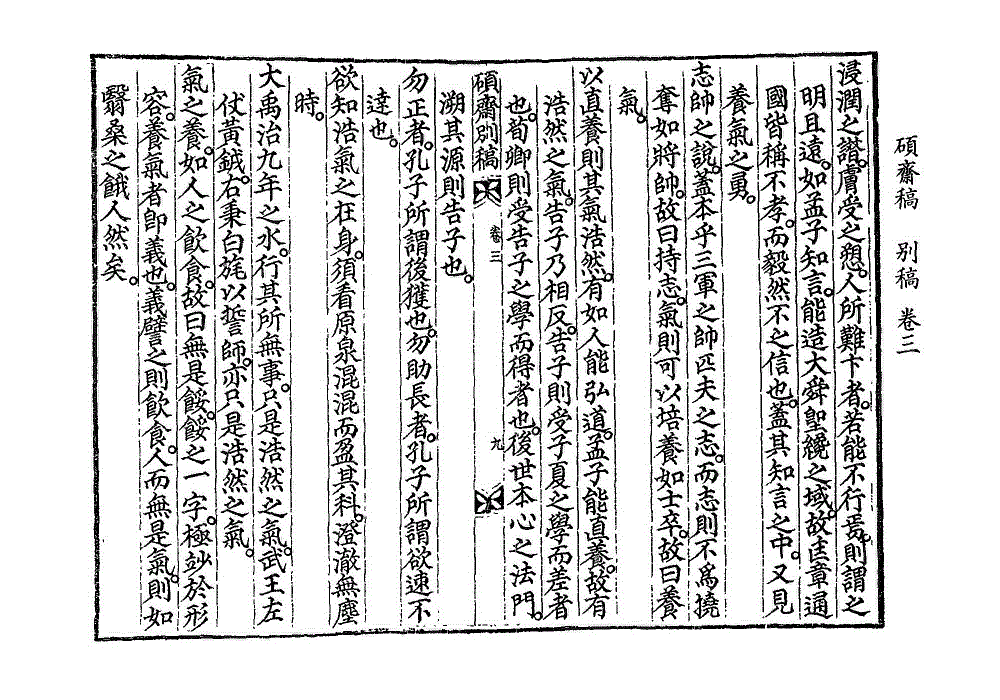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人所难卞者。若能不行焉。则谓之明且远。如孟子知言。能造大舜堲才之域。故匡章通国皆称不孝。而毅然不之信也。盖其知言之中。又见养气之勇。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人所难卞者。若能不行焉。则谓之明且远。如孟子知言。能造大舜堲才之域。故匡章通国皆称不孝。而毅然不之信也。盖其知言之中。又见养气之勇。志帅之说。盖本乎三军之帅匹夫之志。而志则不为挠夺如将帅。故曰持志。气则可以培养如士卒。故曰养气。
以直养则其气浩然。有如人能弘道。孟子能直养。故有浩然之气。告子乃相反。告子则受子夏之学而差者也。荀卿则受告子之学而得者也。后世本心之法门。溯其源则告子也。
勿正者。孔子所谓后获也。勿助长者。孔子所谓欲速不达也。
欲知浩气之在身。须看原泉混混而盈其科。澄澈无尘时。
大禹治九年之水。行其所无事。只是浩然之气。武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誓师。亦只是浩然之气。
气之养。如人之饮食。故曰无是馁。馁之一字。极妙于形容。养气者即义也。义譬之则饮食。人而无是气。则如翳桑之饿人然矣。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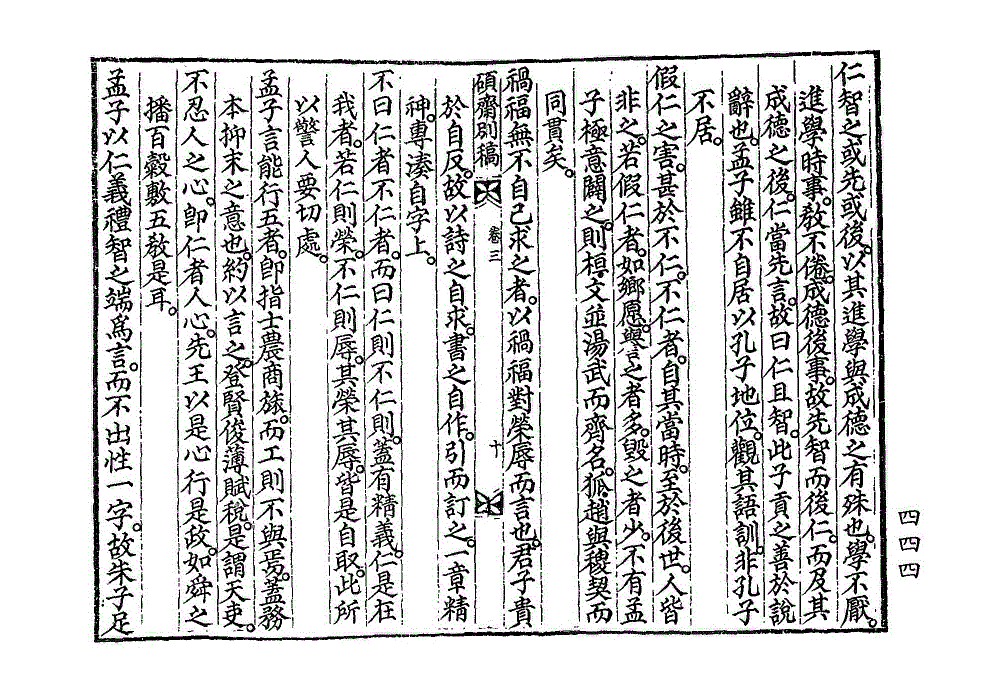 仁智之或先或后。以其进学与成德之有殊也。学不厌。进学时事。教不倦。成德后事。故先智而后仁。而及其成德之后。仁当先言。故曰仁且智。此子贡之善于说辞也。孟子虽不自居以孔子地位。观其语训。非孔子不居。
仁智之或先或后。以其进学与成德之有殊也。学不厌。进学时事。教不倦。成德后事。故先智而后仁。而及其成德之后。仁当先言。故曰仁且智。此子贡之善于说辞也。孟子虽不自居以孔子地位。观其语训。非孔子不居。假仁之害。甚于不仁。不仁者。自其当时。至于后世。人皆非之。若假仁者。如乡愿。誉之者多。毁之者少。不有孟子极意辟之。则桓文并汤武而齐名。狐赵与稷契而同贯矣。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以祸福对荣辱而言也。君子贵于自反。故以诗之自求。书之自作。引而订之。一章精神。专凑自字上。
不曰仁者不仁者。而曰仁则不仁则。盖有精义。仁是在我者。若仁则荣。不仁则辱。其荣其辱。皆是自取。此所以警人要切处。
孟子言能行五者。即指士农商旅。而工则不与焉。盖务本抑末之意也。约以言之。登贤俊薄赋税。是谓天吏。
不忍人之心。即仁者人心。先王以是心行是政。如舜之播百谷敷五教是耳。
孟子以仁义礼智之端为言。而不出性一字。故朱子足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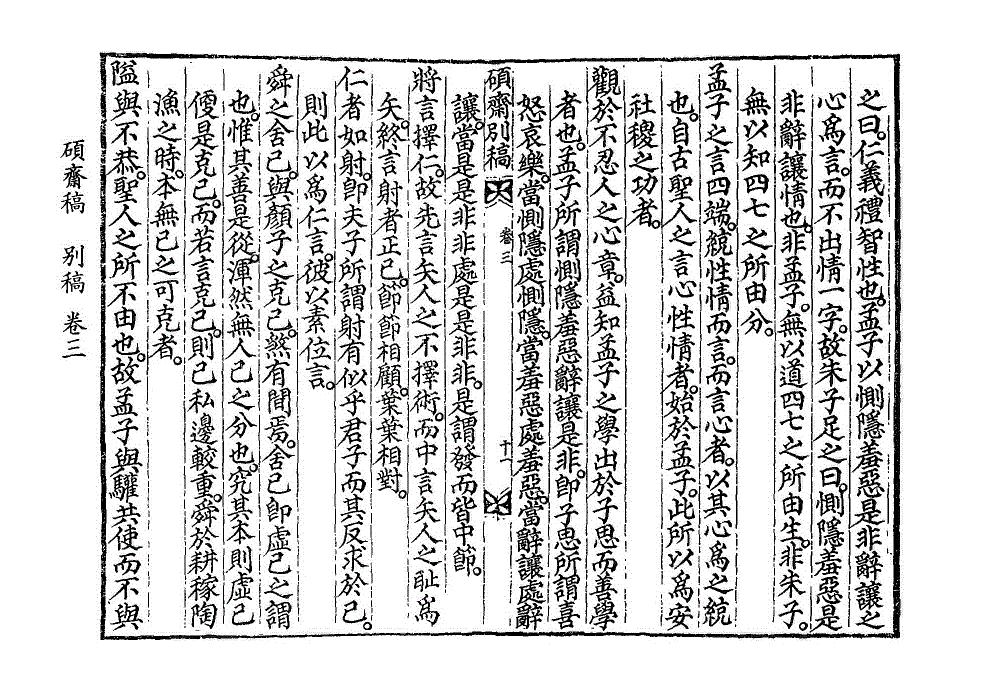 之曰。仁义礼智性也。孟子以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为言。而不出情一字。故朱子足之曰。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情也。非孟子。无以道四七之所由生。非朱子。无以知四七之所由分。
之曰。仁义礼智性也。孟子以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为言。而不出情一字。故朱子足之曰。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情也。非孟子。无以道四七之所由生。非朱子。无以知四七之所由分。孟子之言四端。统性情而言。而言心者。以其心为之统也。自古圣人之言心性情者。始于孟子。此所以为安社稷之功者。
观于不忍人之心章。益知孟子之学出于子思而善学者也。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子思所谓喜怒哀乐。当恻隐处恻隐。当羞恶处羞恶。当辞让处辞让。当是是非非处是是非非。是谓发而皆中节。
将言择仁。故先言矢人之不择术。而中言矢人之耻为矢。终言射者正己。节节相顾。叶叶相对。
仁者如射。即夫子所谓射有似乎君子而其反求于己。则此以为仁言。彼以素位言。
舜之舍己。与颜子之克己。煞有间焉。舍己即虚己之谓也。惟其善是从。浑然无人己之分也。究其本则虚己便是克己。而若言克己。则己私边较重。舜于耕稼陶渔之时。本无己之可克者。
隘与不恭。圣人之所不由也。故孟子与驩共使而不与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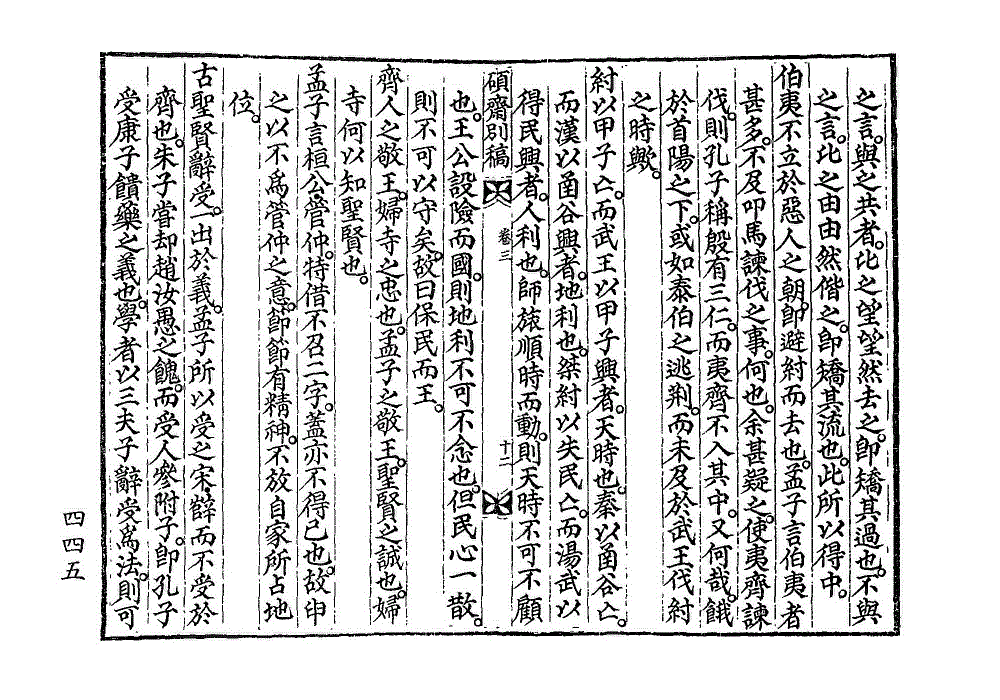 之言。与之共者。比之望望然去之。即矫其过也。不与之言。比之由由然偕之。即矫其流也。此所以得中。
之言。与之共者。比之望望然去之。即矫其过也。不与之言。比之由由然偕之。即矫其流也。此所以得中。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即避纣而去也。孟子言伯夷者甚多。不及叩马谏伐之事。何也。余甚疑之。使夷齐谏伐。则孔子称殷有三仁。而夷齐不入其中。又何哉。饿于首阳之下。或如泰伯之逃荆。而未及于武王伐纣之时欤。
纣以甲子亡。而武王以甲子兴者。天时也。秦以函谷亡。而汉以函谷兴者。地利也。桀纣以失民亡。而汤武以得民兴者。人利也。师旅顺时而动。则天时不可不顾也。王公设险而国。则地利不可不念也。但民心一散。则不可以守矣。故曰保民而王。
齐人之敬王。妇寺之忠也。孟子之敬王。圣贤之诚也。妇寺何以知圣贤也。
孟子言桓公,管仲。特借不召二字。盖亦不得已也。故申之以不为管仲之意。节节有精神。不放自家所占地位。
古圣贤辞受。一出于义。孟子所以受之宋,辥而不受于齐也。朱子尝却赵汝愚之馈。而受人参附子。即孔子受康子馈药之义也。学者以三夫子辞受为法。则可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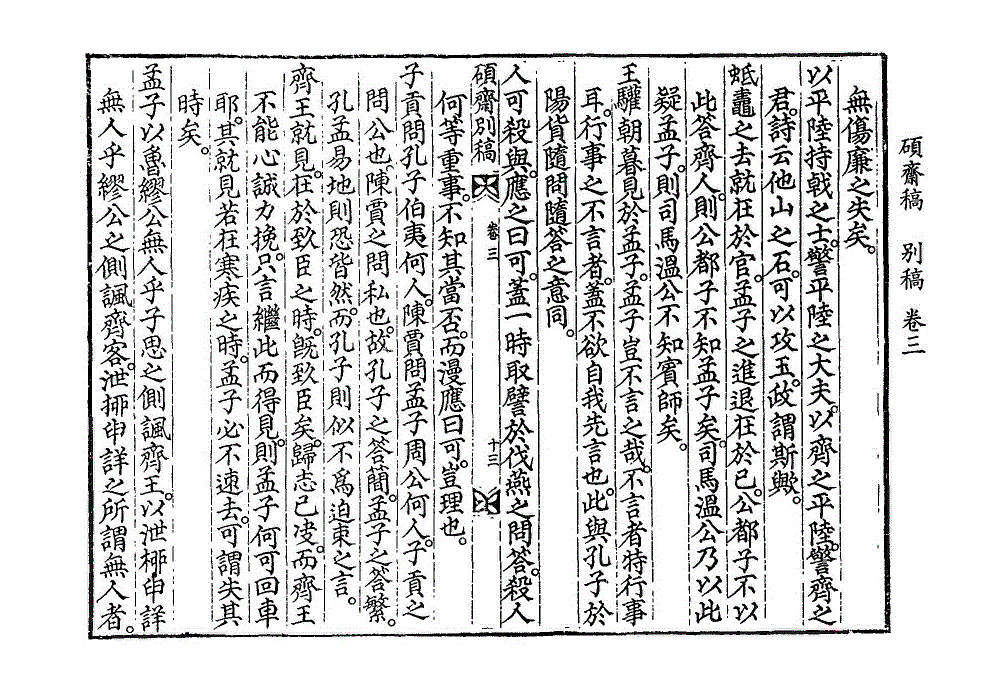 无伤廉之失矣。
无伤廉之失矣。以平陆持戟之士。警平陆之大夫。以齐之平陆。警齐之君。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谓斯欤。
蚳蛙之去就在于官。孟子之进退在于己。公都子不以此答齐人。则公都子不知孟子矣。司马温公乃以此疑孟子。则司马温公不知宾师矣。
王驩朝暮见于孟子。孟子岂不言之哉。不言者特行事耳。行事之不言者。盖不欲自我先言也。此与孔子于阳货随问随答之意同。
人可杀与。应之曰可。盖一时取譬于伐燕之问答。杀人何等重事。不知其当否。而漫应曰可。岂理也。
子贡问孔子伯夷何人。陈贾问孟子周公何人。子贡之问公也。陈贾之问私也。故孔子之答简。孟子之答繁。孔孟易地则恐皆然。而孔子则似不为迫束之言。
齐王就见。在于致臣之时。既致臣矣。归志已决。而齐王不能心诚力挽。只言继此而得见。则孟子何可回车耶。其就见若在寒疾之时。孟子必不速去。可谓失其时矣。
孟子以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讽齐王。以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讽齐客。泄柳,申详之所谓无人者。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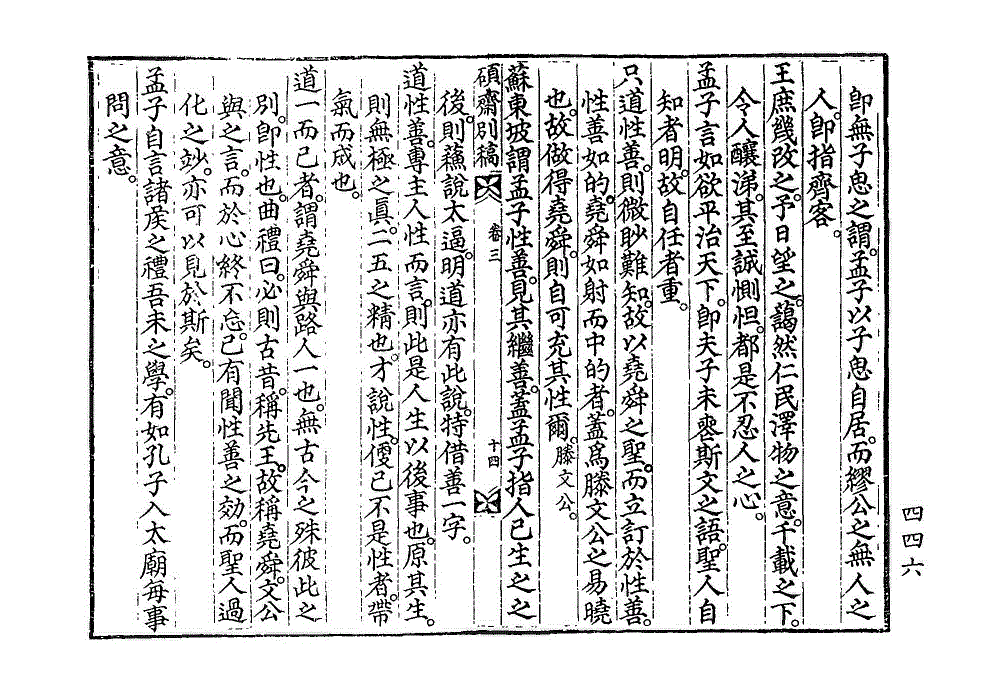 即无子思之谓。孟子以子思自居。而缪公之无人之人。即指齐客。
即无子思之谓。孟子以子思自居。而缪公之无人之人。即指齐客。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蔼然仁民泽物之意。千载之下。令人酿涕。其至诚恻怛。都是不忍人之心。
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即夫子未丧斯文之语。圣人自知者明。故自任者重。
只道性善。则微眇难知。故以尧舜之圣。而立订于性善。性善如的。尧舜如射而中的者。盖为滕文公之易晓也。故做得尧舜。则自可充其性尔。(滕文公。)
苏东坡谓孟子性善。见其继善。盖孟子指人已生之之后。则苏说太逼。明道亦有此说。特借善一字。
道性善。专主人性而言。则此是人生以后事也。原其生。则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也。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者。带气而成也。
道一而已者。谓尧舜与路人一也。无古今之殊彼此之别。即性也。曲礼曰。必则古昔。称先王。故称尧舜。文公与之言。而于心终不忘。已有闻性善之效。而圣人过化之妙。亦可以见于斯矣。
孟子自言诸侯之礼吾未之学。有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之意。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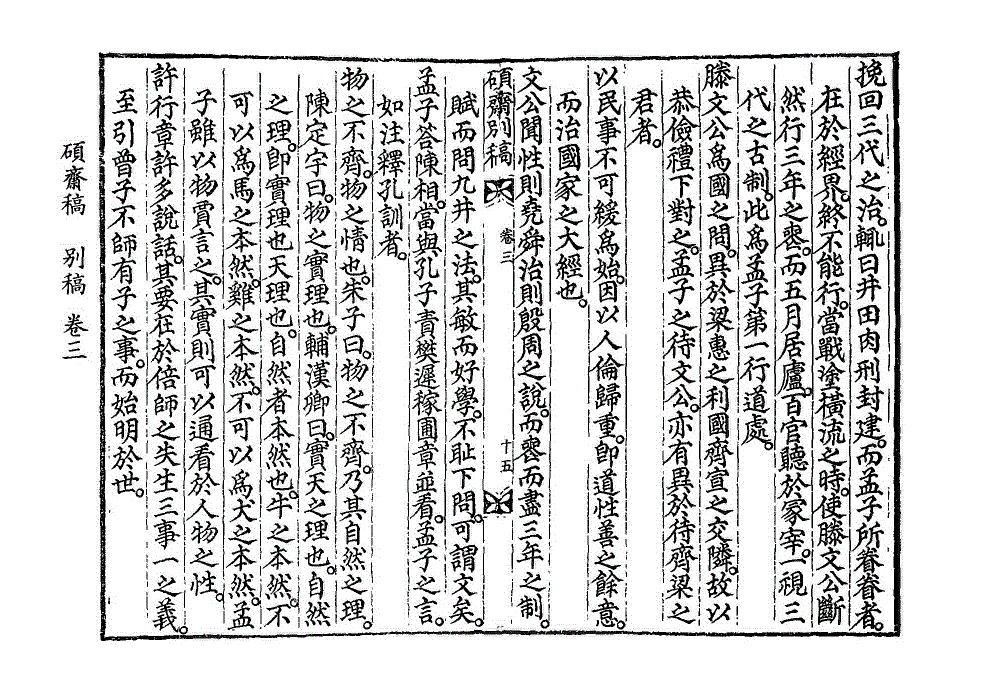 挽回三代之治。辄曰井田肉刑封建。而孟子所眷眷者。在于经界。终不能行。当战涂横流之时。使滕文公断然行三年之丧。而五月居庐。百官听于冢宰。一视三代之古制。此为孟子第一行道处。
挽回三代之治。辄曰井田肉刑封建。而孟子所眷眷者。在于经界。终不能行。当战涂横流之时。使滕文公断然行三年之丧。而五月居庐。百官听于冢宰。一视三代之古制。此为孟子第一行道处。滕文公为国之问。异于梁惠之利国齐宣之交邻。故以恭俭礼下对之。孟子之待文公。亦有异于待齐梁之君者。
以民事不可缓为始。因以人伦归重。即道性善之馀意。而治国家之大经也。
文公闻性则尧舜治则殷周之说。而丧而尽三年之制。赋而问九井之法。其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可谓文矣。
孟子答陈相。当与孔子责樊迟稼圃章并看。孟子之言。如注释孔训者。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朱子曰。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陈定宇曰。物之实理也。辅汉卿曰。实天之理也。自然之理。即实理也天理也。自然者本然也。牛之本然。不可以为马之本然。鸡之本然。不可以为犬之本然。孟子虽以物贾言之。其实则可以通看于人物之性。
许行章许多说话。其要在于倍师之失生三事一之义。至引曾子不师有子之事。而始明于世。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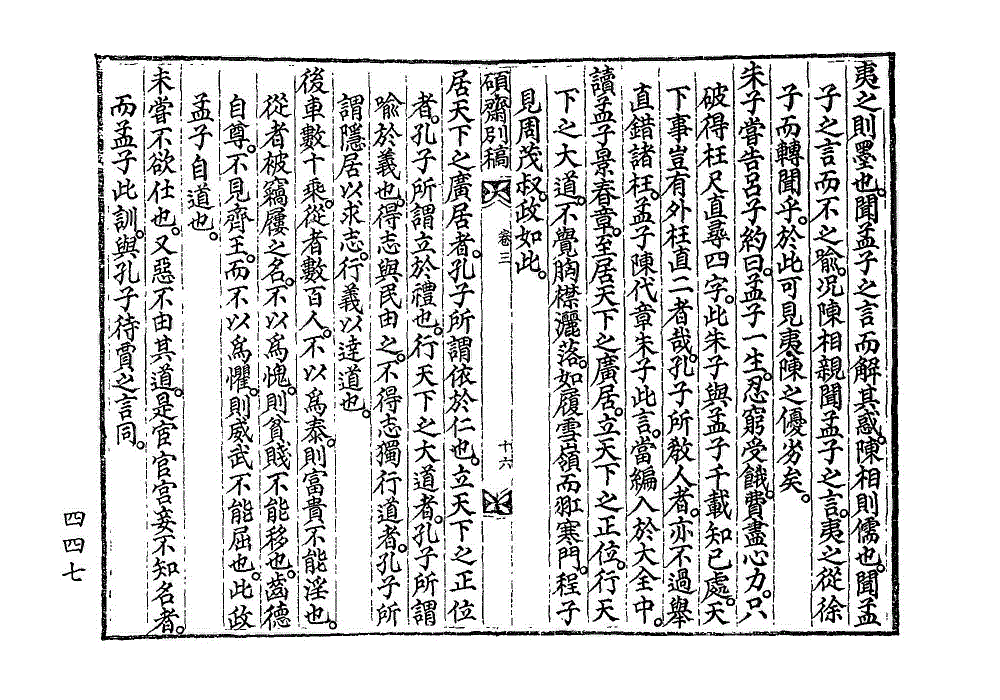 夷之则墨也。闻孟子之言而解其惑。陈相则儒也。闻孟子之言而不之喻。况陈相亲闻孟子之言。夷之从徐子而转闻乎。于此可见夷,陈之优劣矣。
夷之则墨也。闻孟子之言而解其惑。陈相则儒也。闻孟子之言而不之喻。况陈相亲闻孟子之言。夷之从徐子而转闻乎。于此可见夷,陈之优劣矣。朱子尝告吕子约曰。孟子一生。忍穷受饿。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此朱子与孟子千载知己处。天下事岂有外枉直二者哉。孔子所教人者。亦不过举直错诸枉。孟子陈代章朱子此言。当编入于大全中。
读孟子景春章。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觉胸襟洒落。如履雪岭而羾寒门。程子见周茂叔。政如此。
居天下之广居者。孔子所谓依于仁也。立天下之正位者。孔子所谓立于礼也。行天下之大道者。孔子所谓喻于义也。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道者。孔子所谓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也。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不以为泰。则富贵不能淫也。从者被窃屦之名。不以为愧。则贫贱不能移也。齿德自尊。不见齐王。而不以为惧。则威武不能屈也。此政孟子自道也。
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是宦官宫妾不知名者。而孟子此训。与孔子待贾之言同。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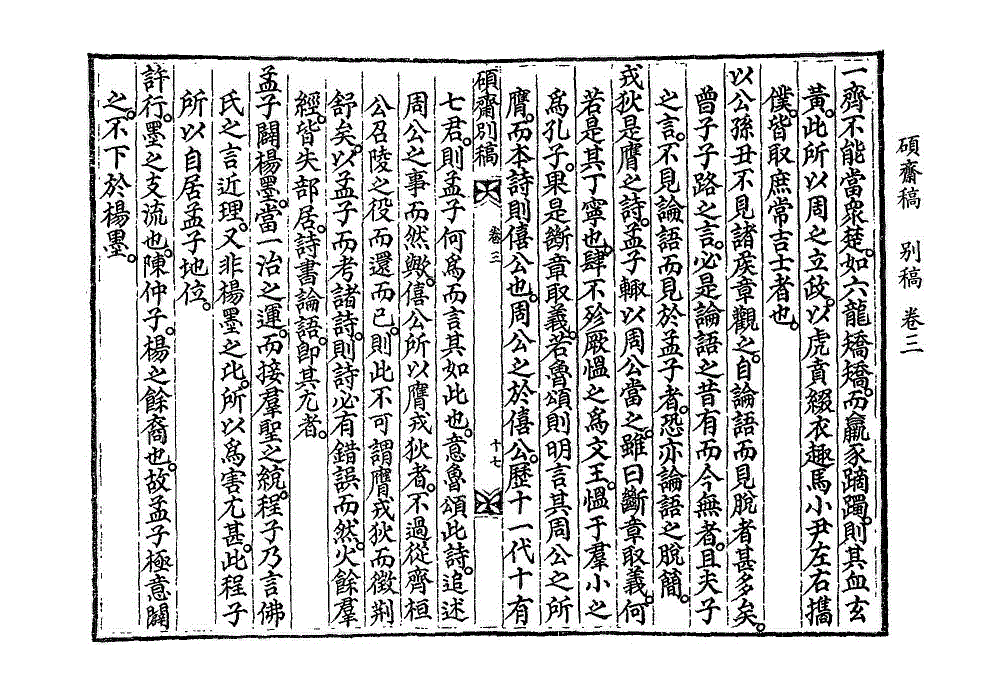 一齐不能当众楚。如六龙矫矫。而羸豕蹢躅。则其血玄黄。此所以周之立政。以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皆取庶常吉士者也。
一齐不能当众楚。如六龙矫矫。而羸豕蹢躅。则其血玄黄。此所以周之立政。以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皆取庶常吉士者也。以公孙丑不见诸侯章观之。自论语而见脱者甚多矣。曾子子路之言。必是论语之昔有而今无者。且夫子之言。不见论语而见于孟子者。恐亦论语之脱简。
戎狄是膺之诗。孟子辄以周公当之。虽曰断章取义。何若是其丁宁也。肆不殄厥愠之为文王。愠于群小之为孔子。果是断章取义。若鲁颂则明言其周公之所膺。而本诗则僖公也。周公之于僖公。历十一代十有七君。则孟子何为而言其如此也。意鲁颂此诗。追述周公之事而然欤。僖公所以膺戎狄者。不过从齐桓公召陵之役而还而已。则此不可谓膺戎狄而徵荆舒矣。以孟子而考诸诗。则诗必有错误而然。火馀群经。皆失部居。诗书论语。即其尤者。
孟子辟杨墨。当一治之运。而接群圣之统。程子乃言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此程子所以自居孟子地位。
许行。墨之支流也。陈仲子。杨之馀裔也。故孟子极意辟之。不下于杨墨。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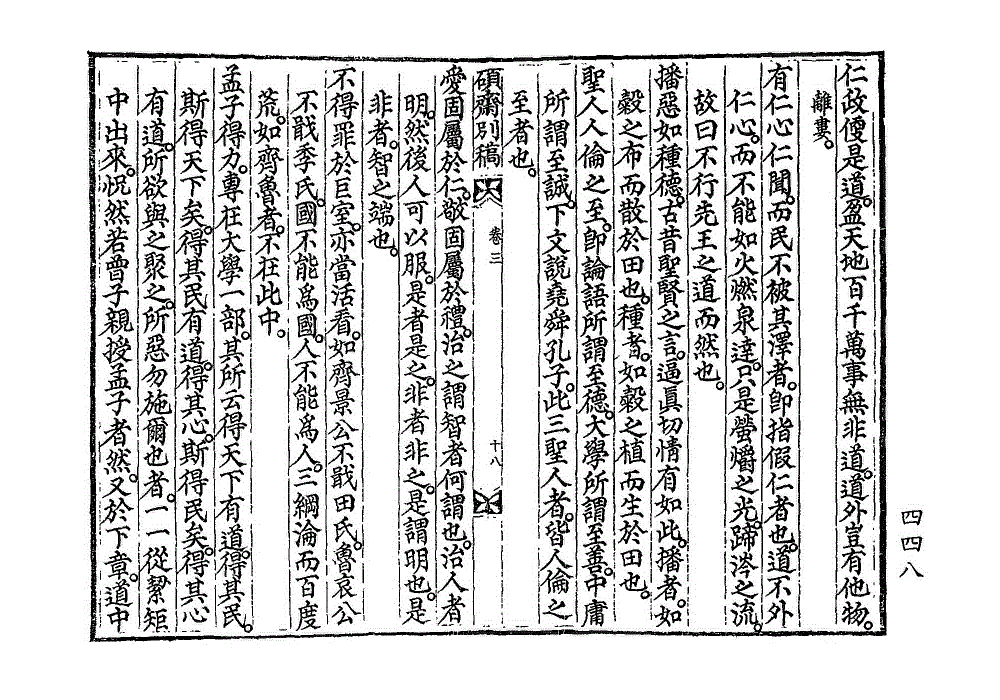 仁政便是道。盈天地百千万事无非道。道外岂有他物。(离娄。)
仁政便是道。盈天地百千万事无非道。道外岂有他物。(离娄。)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即指假仁者也。道不外仁心。而不能如火燃泉达。只是萤爝之光。蹄涔之流。故曰不行先王之道而然也。
播恶如种德。古昔圣贤之言。逼真切情有如此。播者。如谷之布而散于田也。种者。如谷之植而生于田也。
圣人人伦之至。即论语所谓至德。大学所谓至善。中庸所谓至诚。下文说尧舜孔子。此三圣人者。皆人伦之至者也。
爱固属于仁。敬固属于礼。治之谓智者何谓也。治人者明。然后人可以服。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谓明也。是非者。智之端也。
不得罪于巨室。亦当活看。如齐景公不戢田氏。鲁哀公不戢季氏。国不能为国。人不能为人。三纲沦而百度荒。如齐鲁者。不在此中。
孟子得力。专在大学一部。其所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者。一一从絜矩中出来。恍然若曾子亲授孟子者然。又于下章。道中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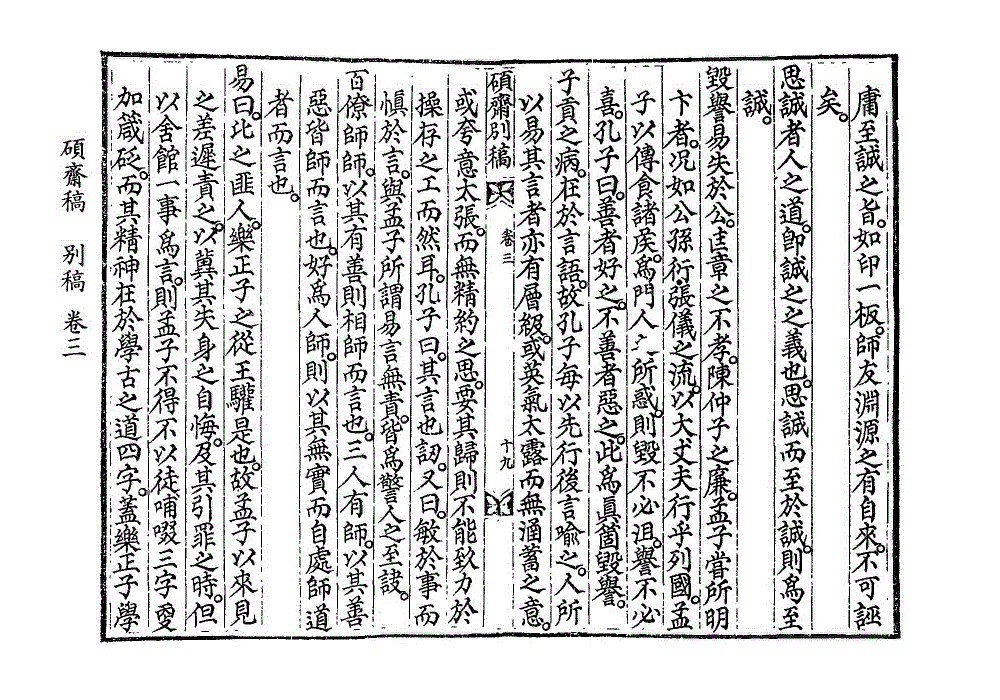 庸至诚之旨。如印一板。师友渊源之有自来。不可诬矣。
庸至诚之旨。如印一板。师友渊源之有自来。不可诬矣。思诚者人之道。即诚之之义也。思诚而至于诚。则为至诚。
毁誉易失于公。匡章之不孝。陈仲子之廉。孟子尝所明卞者。况如公孙衍,张仪之流。以大丈夫行乎列国。孟子以传食诸侯。为门人之所惑。则毁不必沮。誉不必喜。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此为真个毁誉。
子贡之病。在于言语。故孔子每以先行后言喻之。人所以易其言者亦有层级。或英气太露而无涵蓄之意。或夸意太张。而无精约之思。要其归则不能致力于操存之工而然耳。孔子曰。其言也讱。又曰。敏于事而慎于言。与孟子所谓易言无责。皆为警人之至诀。
百僚师师。以其有善则相师而言也。三人有师。以其善恶皆师而言也。好为人师。则以其无实而自处师道者而言也。
易曰。比之匪人。乐正子之从王驩是也。故孟子以来见之差迟责之。以冀其失身之自悔。及其引罪之时。但以舍馆一事为言。则孟子不得不以徒哺啜三字更加箴砭。而其精神在于学古之道四字。盖乐正子学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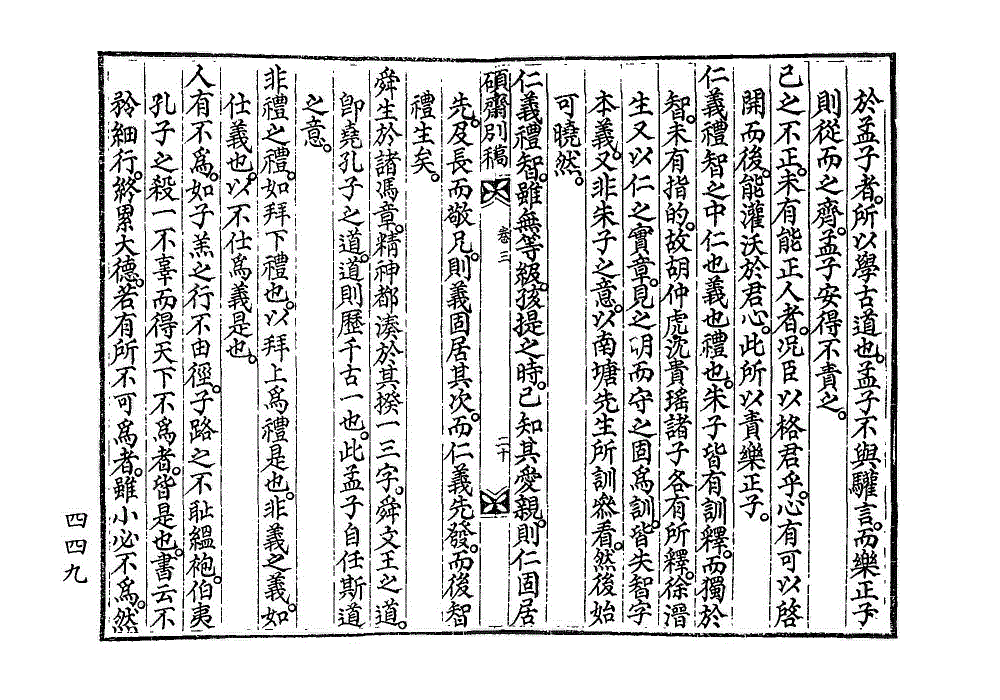 于孟子者。所以学古道也。孟子不与驩言。而乐正子则从而之齐。孟子安得不责之。
于孟子者。所以学古道也。孟子不与驩言。而乐正子则从而之齐。孟子安得不责之。己之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况臣以格君乎。心有可以启开而后。能灌沃于君心。此所以责乐正子。
仁义礼智之中仁也义也礼也。朱子皆有训释。而独于智。未有指的。故胡仲虎,沈贵瑶诸子各有所释。徐溍生又以仁之实章。见之明而守之固为训。皆失智字本义。又非朱子之意。以南塘先生所训参看。然后始可晓然。
仁义礼智。虽无等级。孩提之时。已知其爱亲。则仁固居先。及长而敬兄。则义固居其次。而仁义先发。而后智礼生矣。
舜生于诸冯章。精神都凑于其揆一三字。舜文王之道。即尧孔子之道。道则历千古一也。此孟子自任斯道之意。
非礼之礼。如拜下礼也。以拜上为礼是也。非义之义。如仕义也。以不仕为义是也。
人有不为。如子羔之行不由径。子路之不耻缊袍。伯夷孔子之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皆是也。书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若有所不可为者。虽小必不为。然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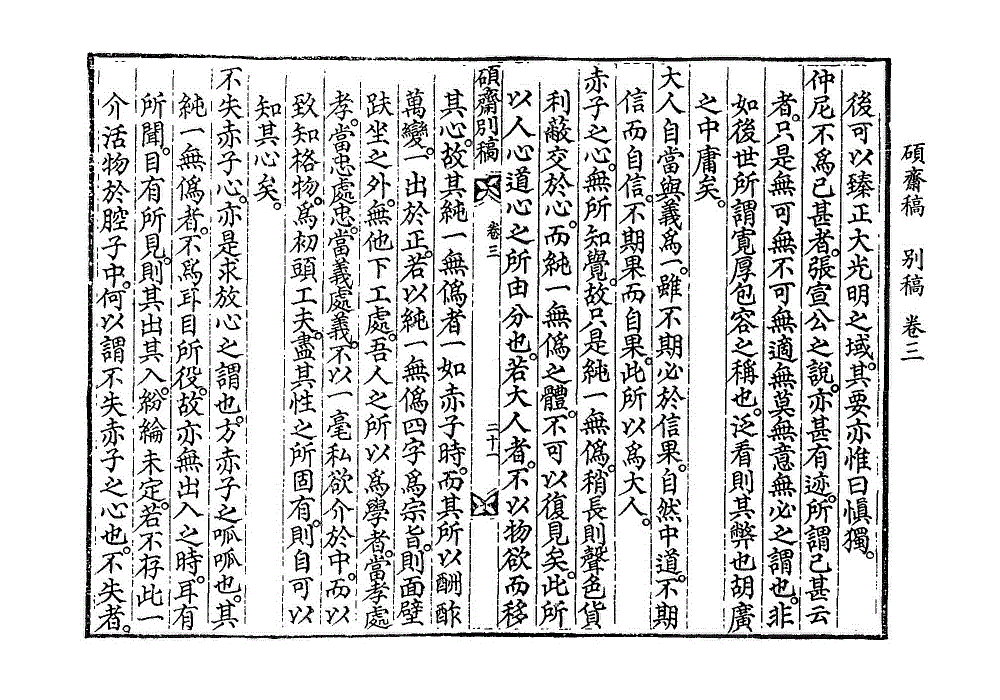 后可以臻正大光明之域。其要亦惟曰慎独。
后可以臻正大光明之域。其要亦惟曰慎独。仲尼不为已甚者。张宣公之说。亦甚有迹。所谓已甚云者。只是无可无不可无适无莫无意无必之谓也。非如后世所谓宽厚包容之称也。泛看则其弊也胡广之中庸矣。
大人自当与义为一。虽不期必于信果。自然中道。不期信而自信。不期果而自果。此所以为大人。
赤子之心。无所知觉。故只是纯一无伪。稍长则声色货利蔽交于心。而纯一无伪之体。不可以复见矣。此所以人心道心之所由分也。若大人者。不以物欲而移其心。故其纯一无伪者一如赤子时。而其所以酬酢万变。一出于正。若以纯一无伪四字为宗旨。则面壁趺坐之外。无他下工处。吾人之所以为学者。当孝处孝。当忠处忠。当义处义。不以一毫私欲介于中。而以致知格物。为初头工夫。尽其性之所固有。则自可以知其心矣。
不失赤子心。亦是求放心之谓也。方赤子之呱呱也。其纯一无伪者。不为耳目所役。故亦无出入之时。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则其出其入。纷纶未定。若不存此一介活物于腔子中。何以谓不失赤子之心也。不失者。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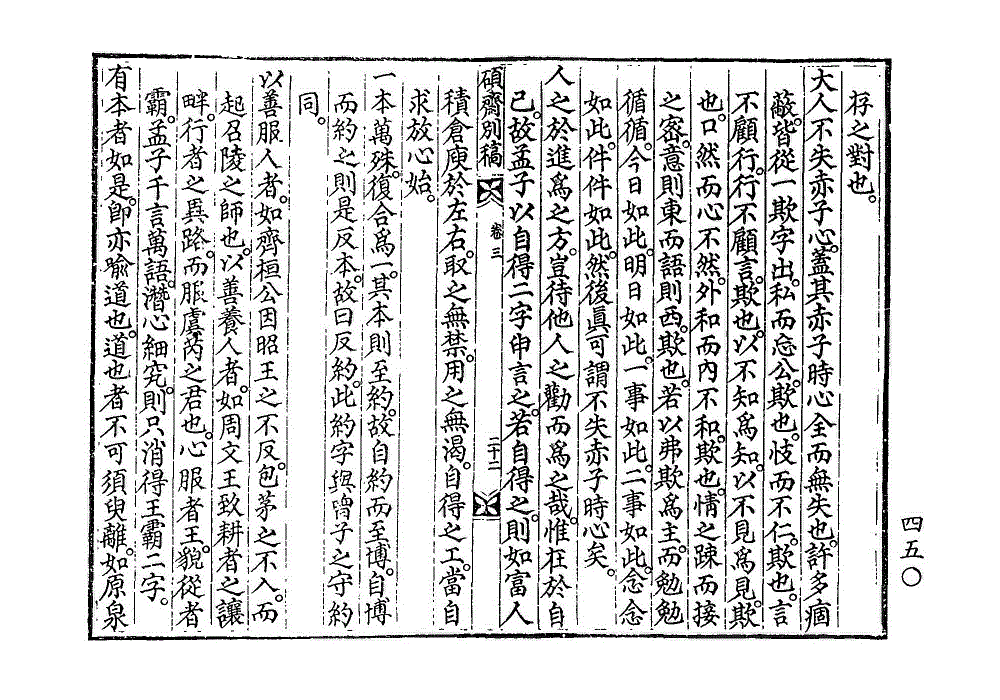 存之对也。
存之对也。大人不失赤子心。盖其赤子时心全而无失也。许多痼蔽。皆从一欺字出。私而忘公。欺也。忮而不仁。欺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欺也。以不知为知。以不见为见。欺也。口然而心不然。外和而内不和。欺也。情之疏而接之密。意则东而语则西。欺也。若以弗欺为主。而勉勉循循。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一事如此。二事如此。念念如此。件件如此。然后真可谓不失赤子时心矣。
人之于进为之方。岂待他人之劝而为之哉。惟在于自己。故孟子以自得二字申言之。若自得之。则如富人积仓庾于左右。取之无禁。用之无渴。自得之工。当自求放心始。
一本万殊。复合为一。其本则至约。故自约而至博。自博而约之则是反本。故曰反约。此约字与曾子之守约同。
以善服人者。如齐桓公因昭王之不反。包茅之不入。而起召陵之师也。以善养人者。如周文王致耕者之让畔。行者之异路。而服虞,芮之君也。心服者王。貌从者霸。孟子千言万语。潜心细究。则只消得王霸二字。
有本者如是。即亦喻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如原泉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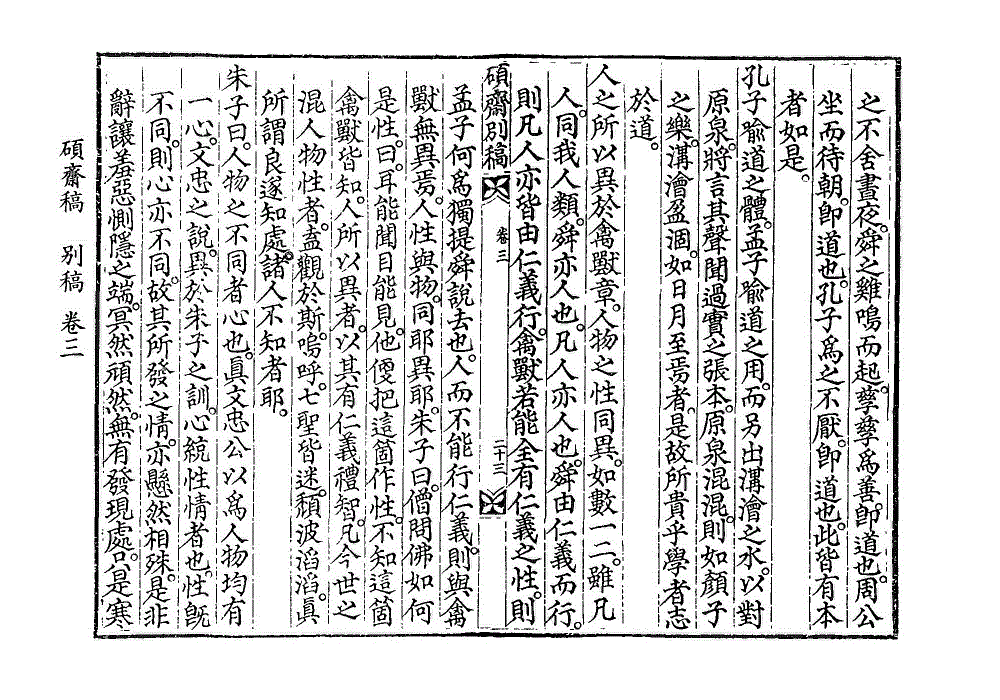 之不舍昼夜。舜之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即道也。周公坐而待朝。即道也。孔子为之不厌。即道也。此皆有本者如是。
之不舍昼夜。舜之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即道也。周公坐而待朝。即道也。孔子为之不厌。即道也。此皆有本者如是。孔子喻道之体。孟子喻道之用。而另出沟浍之水。以对原泉。将言其声闻过实之张本。原泉混混。则如颜子之乐。沟浍盈涸。如日月至焉者。是故所贵乎学者志于道。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人物之性同异。如数一二。虽凡人。同我人类。舜亦人也。凡人亦人也。舜由仁义而行。则凡人亦皆由仁义行。禽兽若能全有仁义之性。则孟子何为独提舜说去也。人而不能行仁义。则与禽兽无异焉。人性与物。同耶异耶。朱子曰。僧问佛如何是性。曰。耳能闻目能见。他便把这个作性。不知这个禽兽皆知。人所以异者。以其有仁义礼智。凡今世之混人物性者。盍观于斯。呜呼。七圣皆迷。颓波滔滔。真所谓良遂知处。诸人不知者耶。
朱子曰。人物之不同者心也。真文忠公以为人物均有一心。文忠之说。异于朱子之训。心统性情者也。性既不同。则心亦不同。故其所发之情。亦悬然相殊。是非辞让羞恶恻隐之端。冥然顽然。无有发现处。只是寒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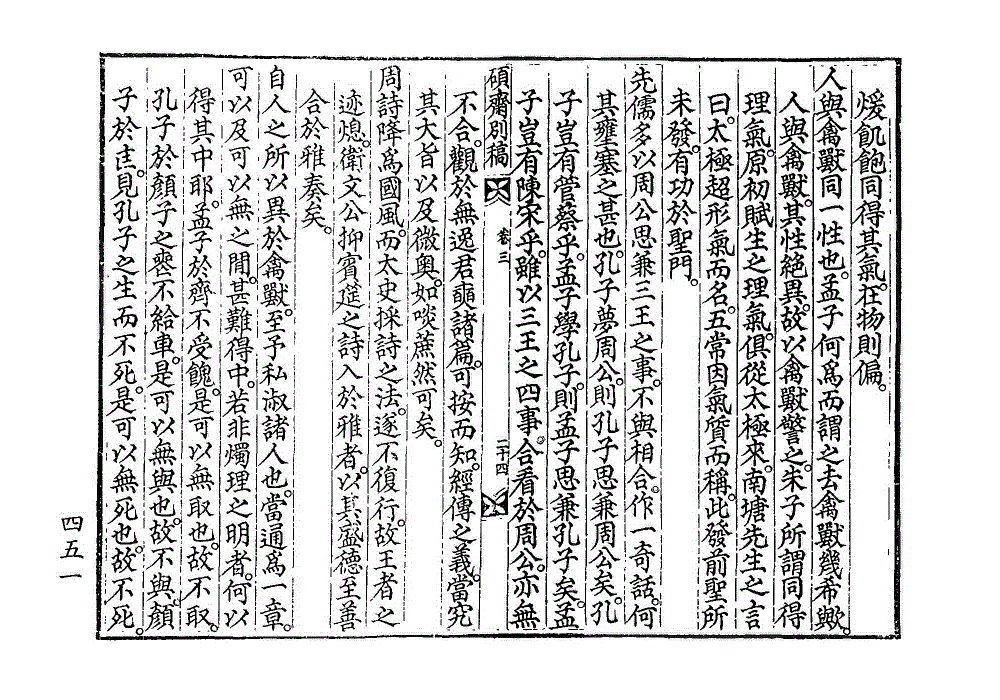 煖饥饱同得其气。在物则偏。
煖饥饱同得其气。在物则偏。人与禽兽同一性也。孟子何为而谓之去禽兽几希欤。人与禽兽。其性绝异。故以禽兽警之。朱子所谓同得理气。原初赋生之理气。俱从太极来。南塘先生之言曰。太极超形气而名。五常因气质而称。此发前圣所未发。有功于圣门。
先儒多以周公思兼三王之事。不与相合。作一奇话。何其壅塞之甚也。孔子梦周公。则孔子思兼周公矣。孔子岂有管,蔡乎。孟子学孔子。则孟子思兼孔子矣。孟子岂有陈,宋乎。虽以三王之四事。合看于周公。亦无不合。观于无逸君奭诸篇。可按而知。经传之义。当究其大旨以及微奥。如啖蔗然可矣。
周诗降为国风。而太史采诗之法。遂不复行。故王者之迹熄。卫文公抑宾筵之诗入于雅者。以其盛德至善合于雅奏矣。
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至予私淑诸人也。当通为一章。
可以及可以无之閒。甚难得中。若非烛理之明者。何以得其中耶。孟子于齐不受馈。是可以无取也。故不取。孔子于颜子之丧不给车。是可以无与也。故不与。颜子于匡。见孔子之生而不死。是可以无死也。故不死。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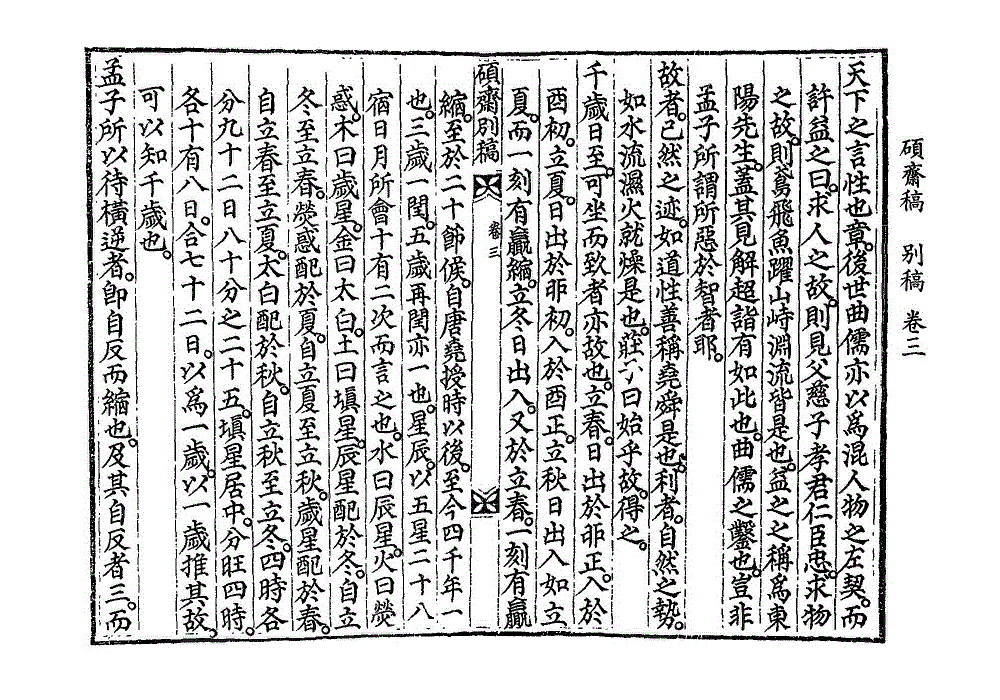 天下之言性也章。后世曲儒亦以为混人物之左契。而许益之曰。求人之故。则见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则鸢飞鱼跃山峙渊流皆是也。益之之称为东阳先生。盖其见解超诣有如此也。曲儒之凿也。岂非孟子所谓所恶于智者耶。
天下之言性也章。后世曲儒亦以为混人物之左契。而许益之曰。求人之故。则见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则鸢飞鱼跃山峙渊流皆是也。益之之称为东阳先生。盖其见解超诣有如此也。曲儒之凿也。岂非孟子所谓所恶于智者耶。故者。已然之迹。如道性善称尧舜是也。利者。自然之势。如水流湿火就燥是也。庄子曰始乎故。得之。
千岁日至。可坐而致者亦故也。立春。日出于卯正。入于酉初。立夏。日出于卯初。入于酉正。立秋日出入如立夏。而一刻有赢缩。立冬日出入。又于立春。一刻有赢缩。至于二十节候。自唐尧授时以后。至今四千年一也。三岁一闰。五岁再闰亦一也。星辰。以五星二十八宿日月所会十有二次而言之也。水曰辰星。火曰荧惑。木曰岁星。金曰太白。土曰填星。辰星配于冬。自立冬至立春。荧惑配于夏。自立夏至立秋。岁星配于春。自立春至立夏。太白配于秋。自立秋至立冬。四时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二十五。填星居中。分旺四时。各十有八日。合七十二日。以为一岁。以一岁推其故。可以知千岁也。
孟子所以待横逆者。即自反而缩也。及其自反者三。而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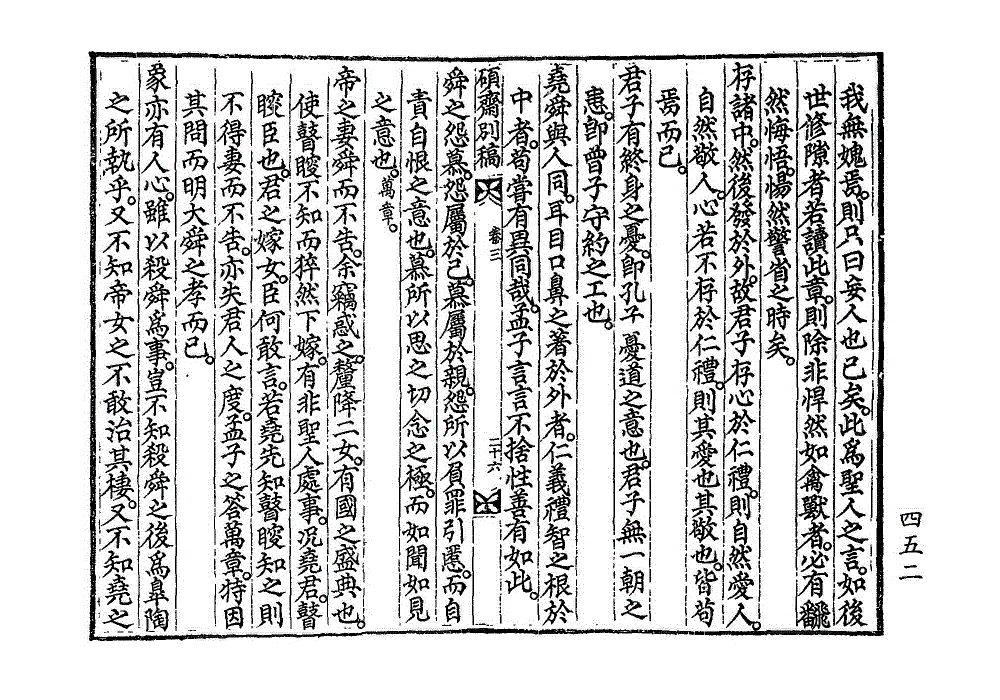 我无愧焉。则只曰妄人也已矣。此为圣人之言。如后世修隙者若读此章。则除非悍然如禽兽者。必有翻然悔悟。惕然警省之时矣。
我无愧焉。则只曰妄人也已矣。此为圣人之言。如后世修隙者若读此章。则除非悍然如禽兽者。必有翻然悔悟。惕然警省之时矣。存诸中。然后发于外。故君子存心于仁礼。则自然爱人。自然敬人。心若不存于仁礼。则其爱也其敬也。皆苟焉而已。
君子有终身之忧。即孔子忧道之意也。君子无一朝之患。即曾子守约之工也。
尧舜与人同。耳目口鼻之著于外者。仁义礼智之根于中者。苟尝有异同哉。孟子言言不舍性善有如此。
舜之怨慕。怨属于己。慕属于亲。怨所以负罪引慝。而自责自恨之意也。慕所以思之切念之极。而如闻如见之意也。(万章。)
帝之妻舜而不告。余窃惑之。釐降二女。有国之盛典也。使瞽瞍不知而猝然下嫁。有非圣人处事。况尧君。瞽瞍臣也。君之嫁女。臣何敢言。若尧先知瞽瞍知之则不得妻而不告。亦失君人之度。孟子之答万章。特因其问而明大舜之孝而已。
象亦有人心。虽以杀舜为事。岂不知杀舜之后为皋陶之所执乎。又不知帝女之不敢治其栖。又不知尧之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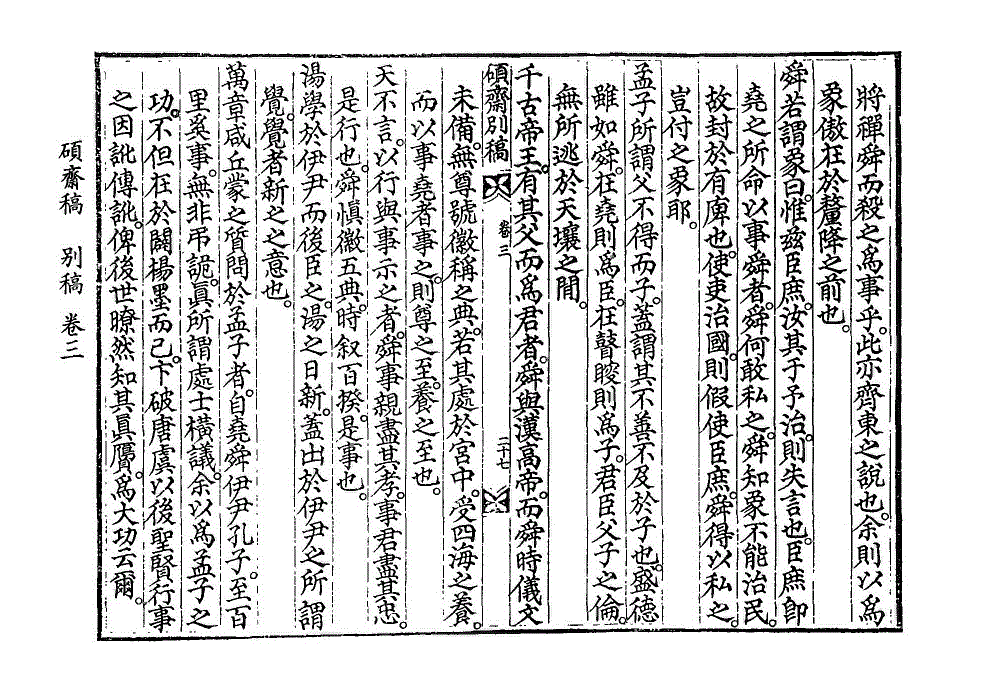 将禅舜而杀之为事乎。此亦齐东之说也。余则以为象傲在于釐降之前也。
将禅舜而杀之为事乎。此亦齐东之说也。余则以为象傲在于釐降之前也。舜若谓象曰。惟玆臣庶。汝其于予治。则失言也。臣庶即尧之所命以事舜者。舜何敢私之。舜知象不能治民。故封于有庳也。使吏治国。则假使臣庶。舜得以私之。岂付之象耶。
孟子所谓父不得而子。盖谓其不善不及于子也。盛德虽如舜。在尧则为臣。在瞽瞍则为子。君臣父子之伦。无所逃于天壤之閒。
千古帝王。有其父而为君者。舜与汉高帝。而舜时仪文未备。无尊号徽称之典。若其处于宫中。受四海之养。而以事尧者事之。则尊之至。养之至也。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者。舜事亲尽其孝。事君尽其忠。是行也。舜慎徽五典。时叙百揆。是事也。
汤学于伊尹而后臣之。汤之日新。盖出于伊尹之所谓觉。觉者新之之意也。
万章咸丘蒙之质问于孟子者。自尧舜伊尹孔子。至百里奚事。无非吊诡。真所谓处士横议。余以为孟子之功。不但在于辟杨墨而已。卞破唐虞以后圣贤行事之因讹传讹。俾后世暸然知其真赝。为大功云尔。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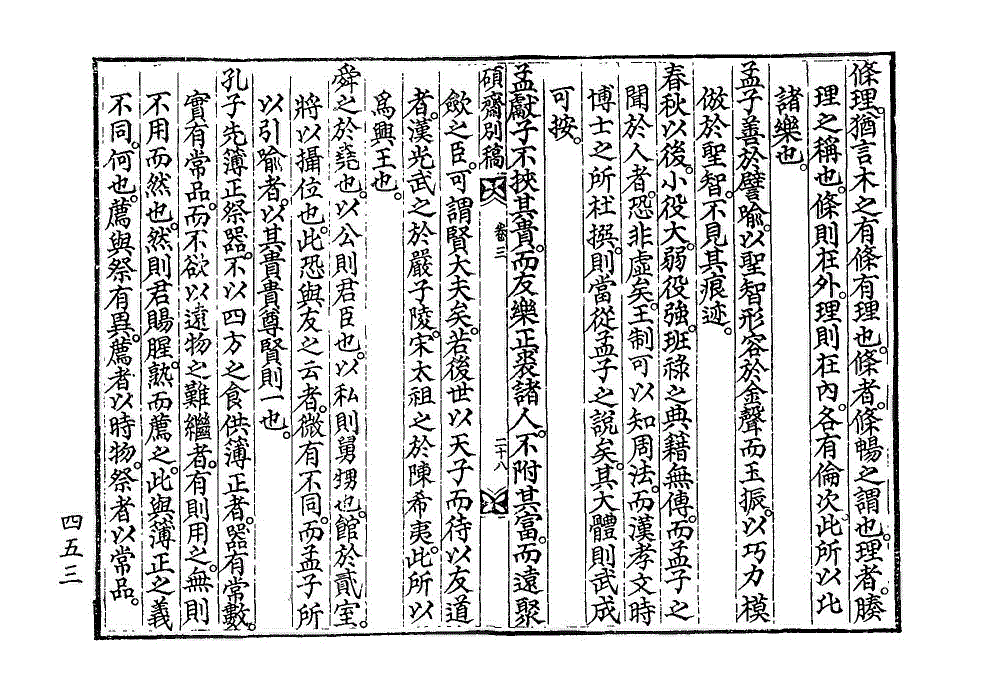 条理。犹言木之有条有理也。条者。条畅之谓也。理者。腠理之称也。条则在外。理则在内。各有伦次。此所以比诸乐也。
条理。犹言木之有条有理也。条者。条畅之谓也。理者。腠理之称也。条则在外。理则在内。各有伦次。此所以比诸乐也。孟子善于譬喻。以圣智形容于金声而玉振。以巧力模仿于圣智。不见其痕迹。
春秋以后。小役大。弱役强。班禄之典籍无传。而孟子之闻于人者。恐非虚矣。王制可以知周法。而汉孝文时博士之所杜撰。则当从孟子之说矣。其大体则武成可按。
孟献子不挟其贵。而友乐正裘诸人。不附其富。而远聚敛之臣。可谓贤大夫矣。若后世以天子而待以友道者。汉光武之于严子陵。宋太祖之于陈希夷。此所以为兴王也。
舜之于尧也。以公则君臣也。以私则舅甥也。馆于贰室。将以摄位也。此恐与友之云者。微有不同。而孟子所以引喻者。以其贵贵尊贤则一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者。器有常数。实有常品。而不欲以远物之难继者。有则用之。无则不用而然也。然则君赐腥。熟而荐之。此与簿正之义不同。何也。荐与祭有异。荐者以时物。祭者以常品。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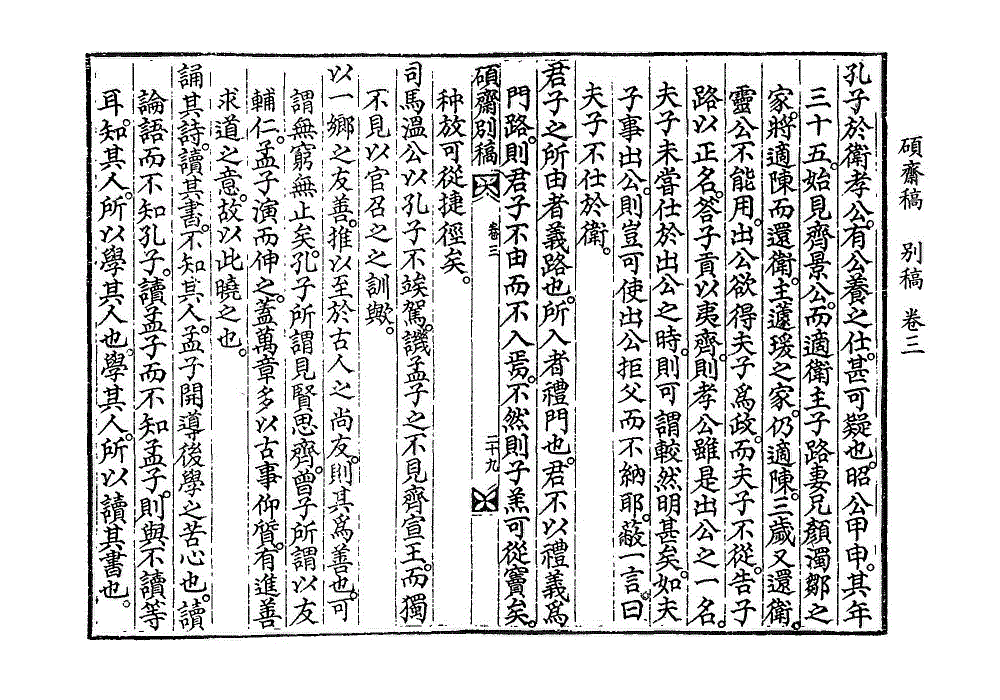 孔子于卫孝公。有公养之仕。甚可疑也。昭公甲申。其年三十五。始见齐景公。而适卫主子路妻兄颜浊邹之家。将适陈而还卫。主蘧瑗之家。仍适陈。三岁又还卫。灵公不能用。出公欲得夫子为政。而夫子不从。告子路以正名。答子贡以夷齐。则孝公虽是出公之一名。夫子未尝仕于出公之时。则可谓较然明甚矣。如夫子事出公。则岂可使出公拒父而不纳耶。蔽一言。曰夫子不仕于卫。
孔子于卫孝公。有公养之仕。甚可疑也。昭公甲申。其年三十五。始见齐景公。而适卫主子路妻兄颜浊邹之家。将适陈而还卫。主蘧瑗之家。仍适陈。三岁又还卫。灵公不能用。出公欲得夫子为政。而夫子不从。告子路以正名。答子贡以夷齐。则孝公虽是出公之一名。夫子未尝仕于出公之时。则可谓较然明甚矣。如夫子事出公。则岂可使出公拒父而不纳耶。蔽一言。曰夫子不仕于卫。君子之所由者义路也。所入者礼门也。君不以礼义为门路。则君子不由而不入焉。不然则子羔可从窦矣。种放可从捷径矣。
司马温公以孔子不俟驾。讥孟子之不见齐宣王。而独不见以官召之之训欤。
以一乡之友善。推以至于古人之尚友。则其为善也。可谓无穷无止矣。孔子所谓见贤思齐。曾子所谓以友辅仁。孟子演而伸之。盖万章多以古事仰质。有进善求道之意。故以此晓之也。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孟子开导后学之苦心也。读论语而不知孔子。读孟子而不知孟子。则与不读等耳。知其人。所以学其人也。学其人。所以读其书也。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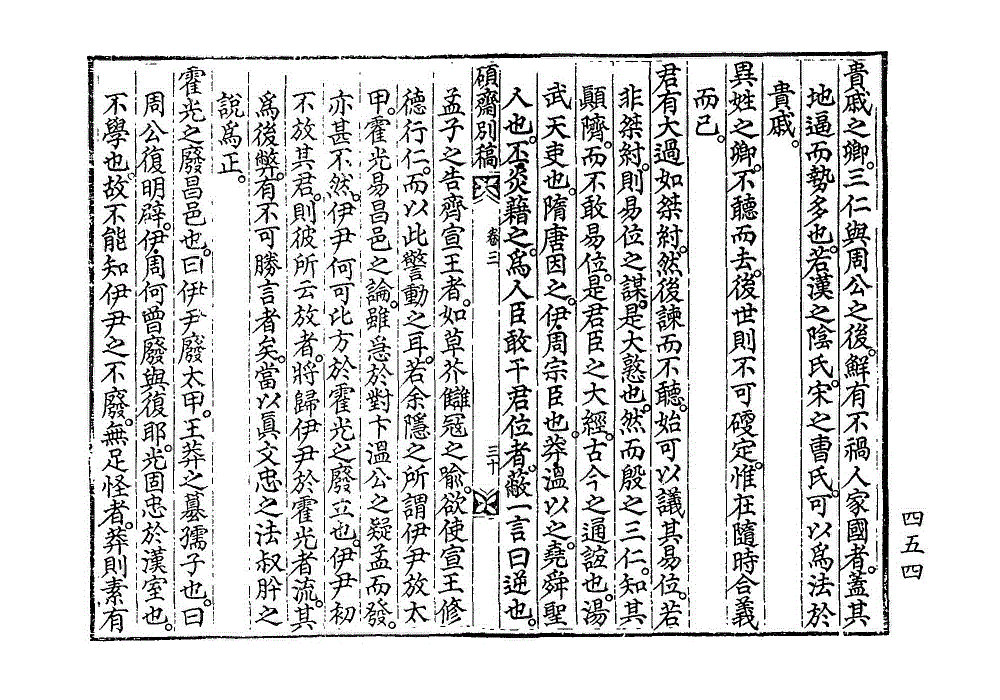 贵戚之卿。三仁与周公之后。鲜有不祸人家国者。盖其地逼而势多也。若汉之阴氏。宋之曹氏。可以为法于贵戚。
贵戚之卿。三仁与周公之后。鲜有不祸人家国者。盖其地逼而势多也。若汉之阴氏。宋之曹氏。可以为法于贵戚。异姓之卿。不听而去。后世则不可硬定。惟在随时合义而已。
君有大过如桀纣。然后谏而不听。始可以议其易位。若非桀纣。则易位之谋。是大憝也。然而殷之三仁。知其颠隮。而不敢易位。是君臣之大经。古今之通谊也。汤武天吏也。隋唐因之。伊,周宗臣也。莽,温以之。尧舜圣人也。丕,炎藉之。为人臣敢干君位者。蔽一言曰逆也。孟子之告齐宣王者。如草芥雠寇之喻。欲使宣王修德行仁。而以此警动之耳。若余隐之所谓伊尹放太甲。霍光易昌邑之论。虽急于对卞温公之疑孟而发。亦甚不然。伊尹何可比方于霍光之废立也。伊尹初不放其君。则彼所云放者。将归伊尹于霍光者流。其为后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当以真文忠之法叔肸之说为正。
霍光之废昌邑也。曰伊尹废太甲。王莽之篡孺子也。曰周公复明辟。伊,周何曾废与复耶。光固忠于汉室也。不学也。故不能知伊尹之不废。无足怪者。莽则素有
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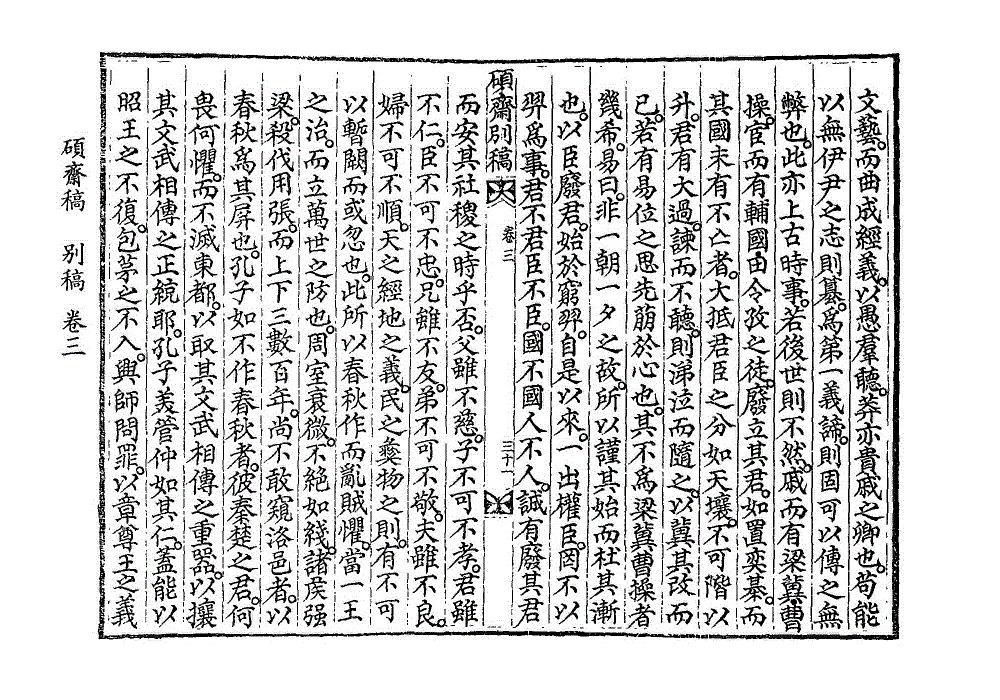 文艺。而曲成经义。以愚群听。莽亦贵戚之卿也。苟能以无伊尹之志则篡。为第一义谛。则固可以传之无弊也。此亦上古时事。若后世则不然。戚而有梁冀,曹操。宦而有辅国,田令孜之徒。废立其君。如置奕棋。而其国未有不亡者。大抵君臣之分如天壤。不可阶以升。君有大过。谏而不听。则涕泣而随之。以冀其改而已。若有易位之思先萌于心也。其不为梁冀曹操者几希。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谨其始而杜其渐也。以臣废君。始于穷羿。自是以来。一出权臣。罔不以羿为事。君不君臣不臣。国不国人不人。诚有废其君而安其社稷之时乎否。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兄虽不友。弟不可不敬。夫虽不良。妇不可不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物之则。有不可以暂阙而或忽也。此所以春秋作而乱贼惧。当一王之治。而立万世之防也。周室衰微。不绝如线。诸侯强梁。杀伐用张。而上下三数百年。尚不敢窥洛邑者。以春秋为其屏也。孔子如不作春秋者。彼秦楚之君。何畏何惧。而不灭东都。以取其文武相传之重器。以攘其文武相传之正统耶。孔子美管仲如其仁。盖能以昭王之不复。包茅之不入。兴师问罪。以章尊王之义
文艺。而曲成经义。以愚群听。莽亦贵戚之卿也。苟能以无伊尹之志则篡。为第一义谛。则固可以传之无弊也。此亦上古时事。若后世则不然。戚而有梁冀,曹操。宦而有辅国,田令孜之徒。废立其君。如置奕棋。而其国未有不亡者。大抵君臣之分如天壤。不可阶以升。君有大过。谏而不听。则涕泣而随之。以冀其改而已。若有易位之思先萌于心也。其不为梁冀曹操者几希。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谨其始而杜其渐也。以臣废君。始于穷羿。自是以来。一出权臣。罔不以羿为事。君不君臣不臣。国不国人不人。诚有废其君而安其社稷之时乎否。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兄虽不友。弟不可不敬。夫虽不良。妇不可不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物之则。有不可以暂阙而或忽也。此所以春秋作而乱贼惧。当一王之治。而立万世之防也。周室衰微。不绝如线。诸侯强梁。杀伐用张。而上下三数百年。尚不敢窥洛邑者。以春秋为其屏也。孔子如不作春秋者。彼秦楚之君。何畏何惧。而不灭东都。以取其文武相传之重器。以攘其文武相传之正统耶。孔子美管仲如其仁。盖能以昭王之不复。包茅之不入。兴师问罪。以章尊王之义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5L 页
 也。虽曰假之云乎。亦有胜于祭足之拒王。重耳之请隧。则圣人之予之。在迹不在心矣。迹则尊王。其心之非真。不可以亿逆而诛之也。孔子曰。君子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孟子曰。引君以当道。吾君不能谓之贼。曲礼曰。礼不踰节。为人臣者。尽其忠而补其过。美则顺而恶则匡。导之于至当之道。则虽有宦戚百十辈。顾何以觊觎神器。易置君位。如汉唐之为哉。谓吾君不可与有为。而敢蓄异图者。是凶逆耳。虽非宦戚。亦足以变乱王纲而涂炭生灵。坤之爻曰。履霜坚冰至。扬子曰。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父子则亲而已矣。君臣则义而已矣。兄弟则友而已矣。夫妇则别而已矣。此理之常也。易位非常也。有非常之人。当非常之时。建非常之功。有如汤武则尚可也。人非汤武。时非㬥虐。功非吊伐则篡也。前乎汤武而有羿,浞。后乎汤武而有莽,操。未闻汤武更有于天下。则圣人非常有也。是以朱子曰。孟子所谓易位。言其理当如是耳。以发明孟子言外之微旨。以诏来人。若以孟朱之言参互而看。其不为弊矣。尧之无为。圣也。老子只见其无为。而不知其钦明文思。故自以为学尧。而至于清虚。禹之
也。虽曰假之云乎。亦有胜于祭足之拒王。重耳之请隧。则圣人之予之。在迹不在心矣。迹则尊王。其心之非真。不可以亿逆而诛之也。孔子曰。君子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孟子曰。引君以当道。吾君不能谓之贼。曲礼曰。礼不踰节。为人臣者。尽其忠而补其过。美则顺而恶则匡。导之于至当之道。则虽有宦戚百十辈。顾何以觊觎神器。易置君位。如汉唐之为哉。谓吾君不可与有为。而敢蓄异图者。是凶逆耳。虽非宦戚。亦足以变乱王纲而涂炭生灵。坤之爻曰。履霜坚冰至。扬子曰。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父子则亲而已矣。君臣则义而已矣。兄弟则友而已矣。夫妇则别而已矣。此理之常也。易位非常也。有非常之人。当非常之时。建非常之功。有如汤武则尚可也。人非汤武。时非㬥虐。功非吊伐则篡也。前乎汤武而有羿,浞。后乎汤武而有莽,操。未闻汤武更有于天下。则圣人非常有也。是以朱子曰。孟子所谓易位。言其理当如是耳。以发明孟子言外之微旨。以诏来人。若以孟朱之言参互而看。其不为弊矣。尧之无为。圣也。老子只见其无为。而不知其钦明文思。故自以为学尧。而至于清虚。禹之硕斋别稿卷之三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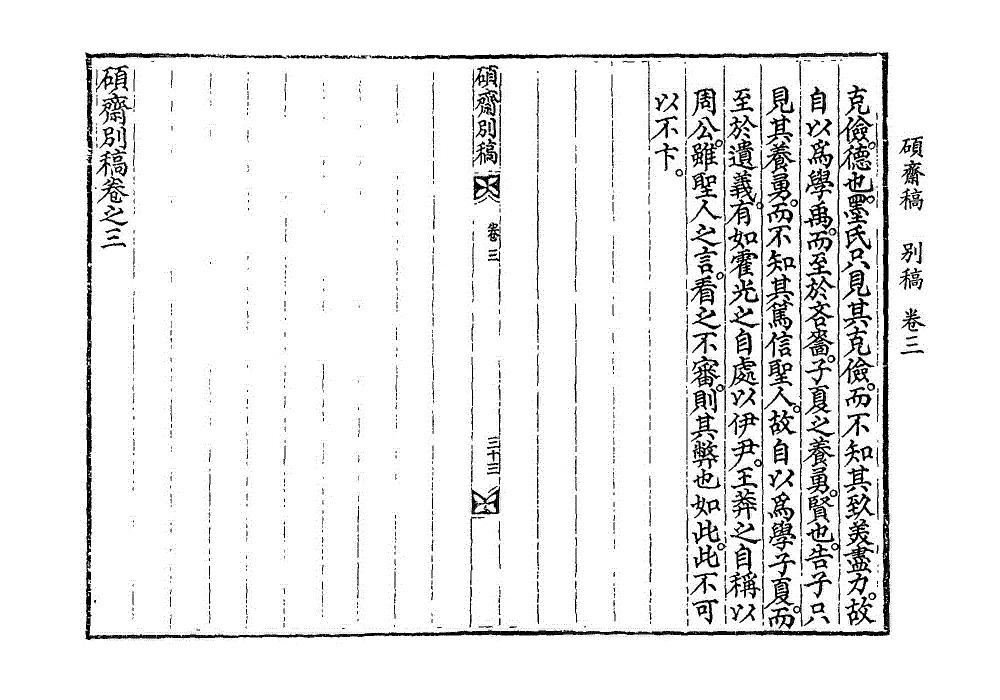 克俭。德也。墨氏只见其克俭。而不知其致美尽力。故自以为学禹。而至于吝啬。子夏之养勇。贤也。告子只见其养勇。而不知其笃信圣人。故自以为学子夏。而至于遗义。有如霍光之自处以伊尹。王莽之自称以周公。虽圣人之言。看之不审。则其弊也如此。此不可以不卞。
克俭。德也。墨氏只见其克俭。而不知其致美尽力。故自以为学禹。而至于吝啬。子夏之养勇。贤也。告子只见其养勇。而不知其笃信圣人。故自以为学子夏。而至于遗义。有如霍光之自处以伊尹。王莽之自称以周公。虽圣人之言。看之不审。则其弊也如此。此不可以不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