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x 页
硕斋别稿卷之二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读论语九篇。不能经意。只事信笔。而比之童习。粗有所得。此所以学贵讲熟也。矮檐烈阳。手卷就阴。无久坐之顷。才坐旋起。日十数。夜欲对松灯翻阅。而蚊蜹四至。亦不能如意。是甚愤也。北方唇舌。付之膜外。便觉无事。因始第十篇。
薪湖随笔
[薪湖随笔]
读论语九篇。不能经意。只事信笔。而比之童习。粗有所得。此所以学贵讲熟也。矮檐烈阳。手卷就阴。无久坐之顷。才坐旋起。日十数。夜欲对松灯翻阅。而蚊蜹四至。亦不能如意。是甚愤也。北方唇舌。付之膜外。便觉无事。因始第十篇。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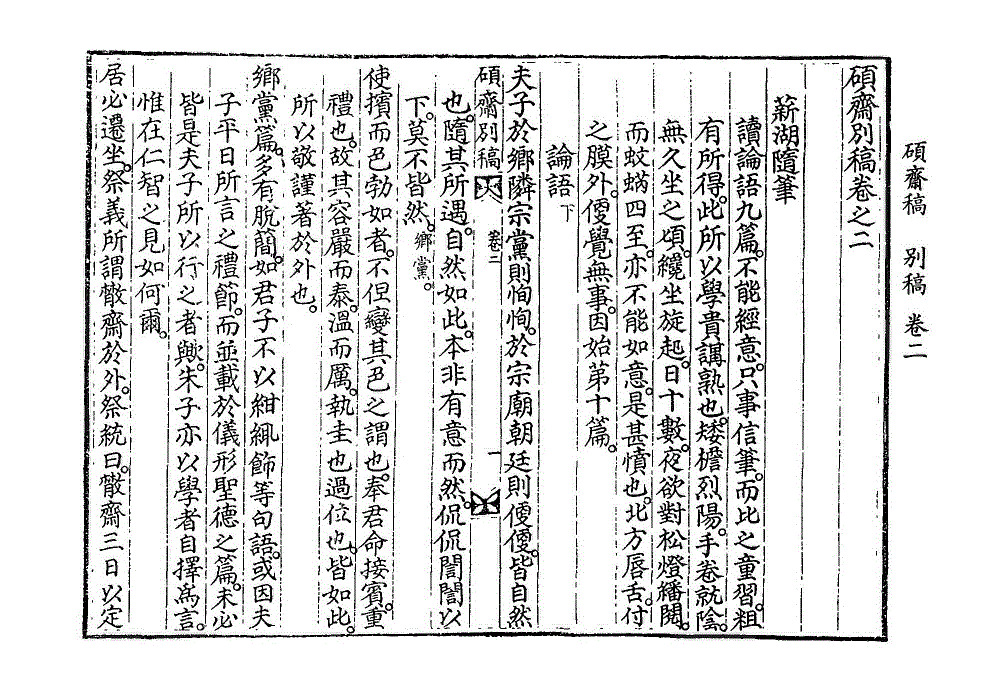 论语[下]
论语[下]夫子于乡邻宗党则恂恂。于宗庙朝廷则便便。皆自然也。随其所遇。自然如此。本非有意而然。侃侃訚訚以下。莫不皆然。(乡党。)
使摈而色勃如者。不但变其色之谓也。奉君命接宾。重礼也。故其容严而泰。温而厉。执圭也过位也。皆如此。所以敬谨著于外也。
乡党篇。多有脱简。如君子不以绀緅饰等句语。或因夫子平日所言之礼节。而并载于仪形圣德之篇。未必皆是夫子所以行之者欤。朱子亦以学者自择为言。惟在仁智之见如何尔。
居必迁坐。祭义所谓散斋于外。祭统曰。散斋三日以定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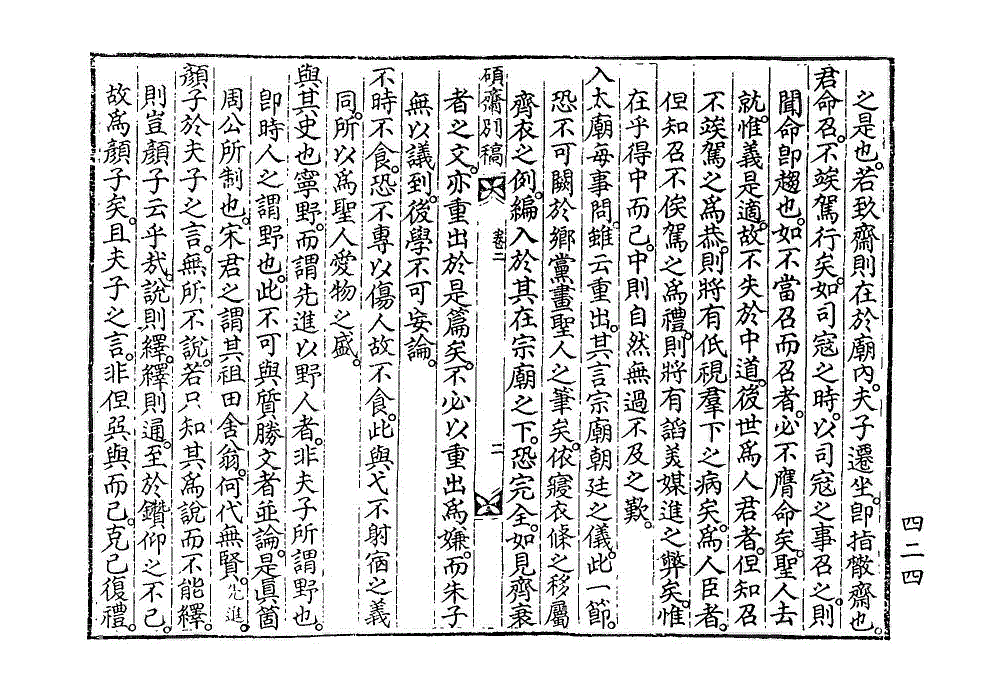 之是也。若致斋则在于庙内。夫子迁坐。即指散斋也。
之是也。若致斋则在于庙内。夫子迁坐。即指散斋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如司寇之时。以司寇之事召之。则闻命即趋也。如不当召而召者。必不膺命矣。圣人去就。惟义是适。故不失于中道。后世为人君者。但知召不俟驾之为恭。则将有低视群下之病矣。为人臣者。但知召不俟驾之为礼。则将有谄美媒进之弊矣。惟在乎得中而已。中则自然无过不及之叹。
入太庙每事问。虽云重出。其言宗庙朝廷之仪。此一节。恐不可阙于乡党画圣人之笔矣。依寝衣条之移属齐衣之例。编入于其在宗庙之下。恐完全。如见齐衰者之文。亦重出于是篇矣。不必以重出为嫌。而朱子无以议到。后学不可妄论。
不时不食。恐不专以伤人故不食。此与弋不射宿之义同。所以为圣人爱物之盛。
与其史也宁野。而谓先进以野人者。非夫子所谓野也。即时人之谓野也。此不可与质胜文者并论。是真个周公所制也。宋君之谓其祖田舍翁。何代无贤。(先进。)
颜子于夫子之言。无所不说。若只知其为说而不能绎。则岂颜子云乎哉。说则绎。绎则通。至于钻仰之不已。故为颜子矣。且夫子之言。非但巽与而已。克己复礼。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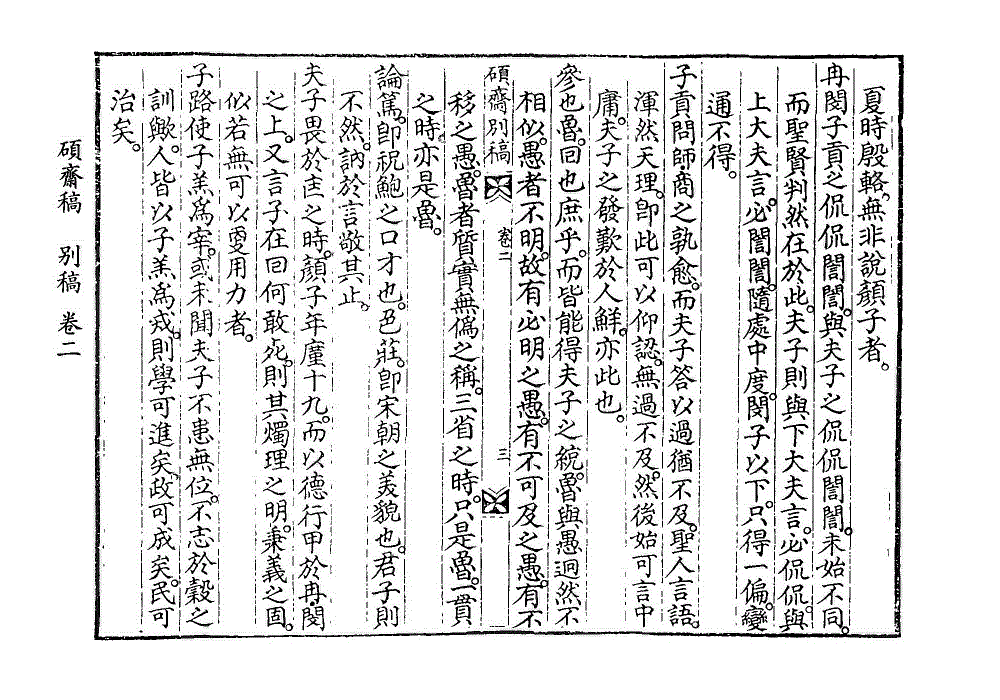 夏时殷辂。无非说颜子者。
夏时殷辂。无非说颜子者。冉闵子贡之侃侃訚訚。与夫子之侃侃訚訚。未始不同。而圣贤判然在于此。夫子则与下大夫言。必侃侃。与上大夫言。必訚訚。随处中度。闵子以下。只得一偏。变通不得。
子贡问师,商之孰愈。而夫子答以过犹不及。圣人言语。浑然天理。即此可以仰认。无过不及。然后始可言中庸。夫子之发叹于人鲜。亦此也。
参也鲁。回也庶乎。而皆能得夫子之统。鲁与愚迥然不相似。愚者不明。故有必明之愚。有不可及之愚。有不移之愚。鲁者质实无伪之称。三省之时。只是鲁。一贯之时。亦是鲁。
论笃。即祝鲍之口才也。色庄。即宋朝之美貌也。君子则不然。讷于言敬其止。
夫子畏于匡之时。颜子年廑十九。而以德行甲于冉,闵之上。又言子在回何敢死。则其烛理之明。秉义之固。似若无可以更用力者。
子路使子羔为宰。或未闻夫子不患无位。不志于谷之训欤。人皆以子羔为戒。则学可进矣。政可成矣。民可治矣。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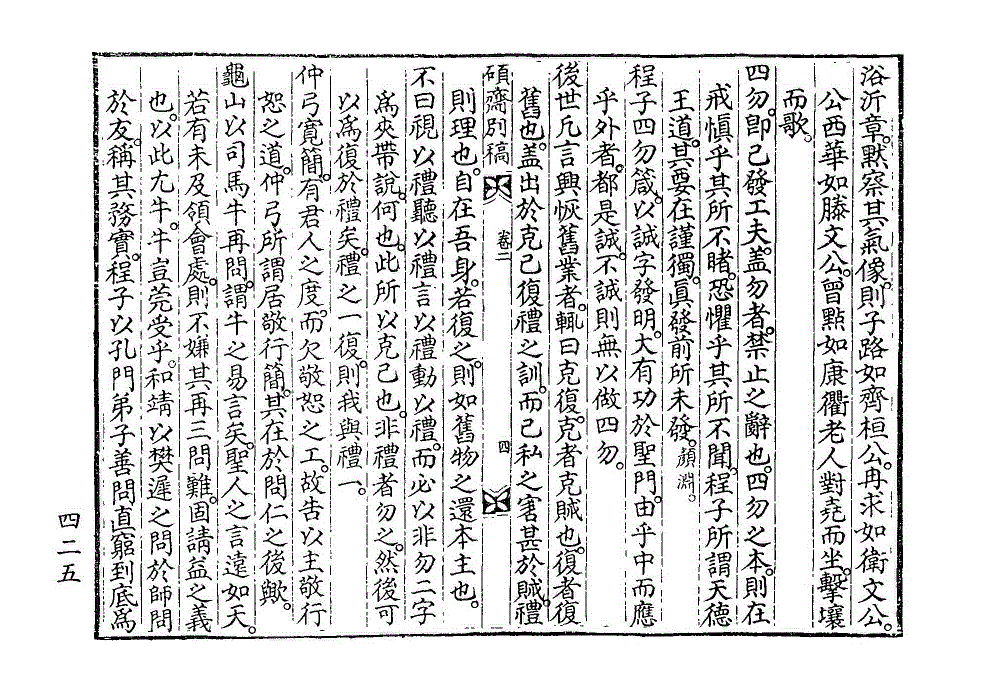 浴沂章。默察其气像。则子路如齐桓公。冉求如卫文公。公西华如滕文公。曾点如康衢老人对尧而坐。击壤而歌。
浴沂章。默察其气像。则子路如齐桓公。冉求如卫文公。公西华如滕文公。曾点如康衢老人对尧而坐。击壤而歌。四勿。即已发工夫。盖勿者。禁止之辞也。四勿之本。则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程子所谓天德王道。其要在谨独。真发前所未发。(颜渊。)
程子四勿箴。以诚字发明。大有功于圣门。由乎中而应乎外者。都是诚。不诚则无以做四勿。
后世凡言兴恢旧业者。辄曰克复。克者克贼也。复者复旧也。盖出于克己复礼之训。而己私之害甚于贼。礼则理也。自在吾身。若复之。则如旧物之还本主也。
不曰视以礼听以礼言以礼动以礼。而必以非勿二字为夹带说。何也。此所以克己也。非礼者勿之。然后可以为复于礼矣。礼之一复。则我与礼一。
仲弓宽简。有君人之度。而欠敬恕之工。故告以主敬行恕之道。仲弓所谓居敬行简。其在于问仁之后欤。
龟山以司马牛再问。谓牛之易言矣。圣人之言远如天。若有未及领会处。则不嫌其再三问难。固请益之义也。以此尤牛。牛岂莞受乎。和靖以樊迟之问于师问于友。称其务实。程子以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为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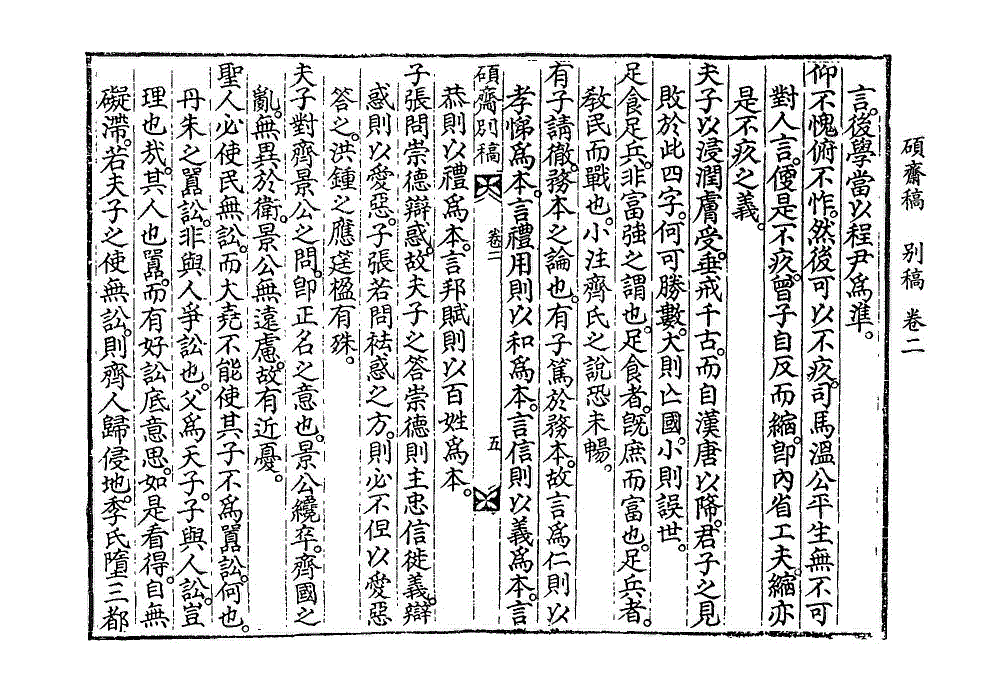 言。后学当以程尹为准。
言。后学当以程尹为准。仰不愧俯不怍。然后可以不疚。司马温公平生无不可对人言。便是不疚。曾子自反而缩。即内省工夫。缩亦是不疚之义。
夫子以浸润肤受。垂戒千古。而自汉唐以降。君子之见败于此四字。何可胜数。大则亡国。小则误世。
足食足兵。非富强之谓也。足食者。既庶而富也。足兵者。教民而战也。小注齐氏之说恐未畅。
有子请彻。务本之论也。有子笃于务本。故言为仁则以孝悌为本。言礼用则以和为本。言信则以义为本。言恭则以礼为本。言邦赋则以百姓为本。
子张问崇德辩惑。故夫子之答崇德则主忠信徙义。辩惑则以爱恶。子张若问袪惑之方。则必不但以爱恶答之。洪钟之应筳(一作莛)楹有殊。
夫子对齐景公之问。即正名之意也。景公才卒。齐国之乱。无异于卫。景公无远虑。故有近忧。
圣人必使民无讼。而大尧不能使其子不为嚣讼。何也。丹朱之嚣讼。非与人争讼也。父为天子。子与人讼。岂理也哉。其人也嚣。而有好讼底意思。如是看得。自无碍滞。若夫子之使无讼。则齐人归侵地。季氏堕三都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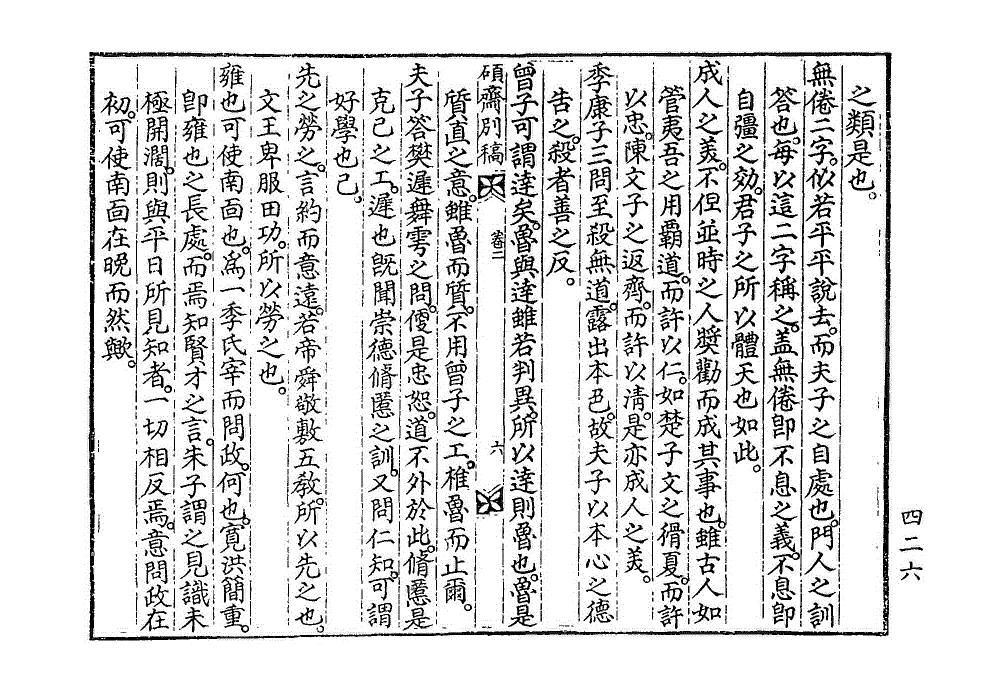 之类是也。
之类是也。无倦二字。似若平平说去。而夫子之自处也。门人之训答也。每以这二字称之。盖无倦即不息之义。不息即自彊之效。君子之所以体天也如此。
成人之美。不但并时之人奖劝而成其事也。虽古人如管夷吾之用霸道。而许以仁。如楚子文之猾夏。而许以忠。陈文子之返齐。而许以清。是亦成人之美。
季康子三问至杀无道。露出本色。故夫子以本心之德告之。杀者善之反。
曾子可谓达矣。鲁与达虽若判异。所以达则鲁也。鲁是质直之意。虽鲁而质。不用曾子之工。椎鲁而止尔。
夫子答樊迟舞雩之问。便是忠恕。道不外于此。脩慝是克己之工。迟也既闻崇德脩慝之训。又问仁知。可谓好学也已。
先之劳之。言约而意远。若帝舜敬敷五教。所以先之也。文王卑服田功。所以劳之也。
雍也可使南面也。为一季氏宰而问政。何也。宽洪简重。即雍也之长处。而焉知贤才之言。朱子谓之见识未极开阔。则与平日所见知者。一切相反焉。意问政在初。可使南面在晚而然欤。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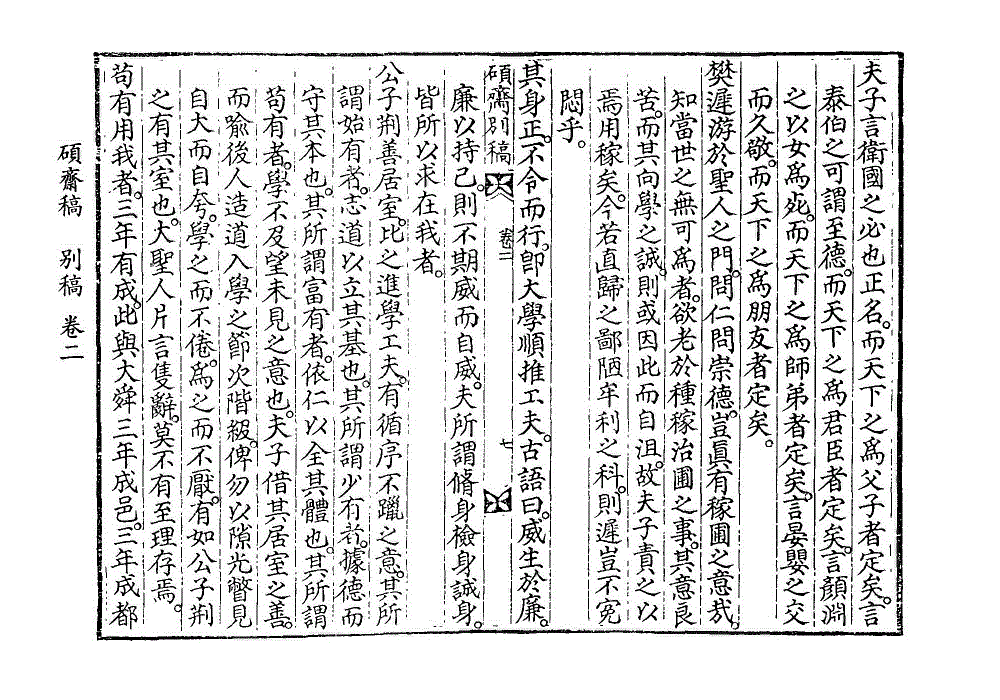 夫子言卫国之必也正名。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矣。言泰伯之可谓至德。而天下之为君臣者定矣。言颜渊之以女为死。而天下之为师弟者定矣。言晏婴之交而久敬。而天下之为朋友者定矣。
夫子言卫国之必也正名。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矣。言泰伯之可谓至德。而天下之为君臣者定矣。言颜渊之以女为死。而天下之为师弟者定矣。言晏婴之交而久敬。而天下之为朋友者定矣。樊迟游于圣人之门。问仁问崇德。岂真有稼圃之意哉。知当世之无可为者。欲老于种稼治圃之事。其意良苦。而其向学之诚。则或因此而自沮。故夫子责之以焉用稼矣。今若直归之鄙陋牟利之科。则迟岂不冤闷乎。
其身正。不令而行。即大学顺推工夫。古语曰。威生于廉。廉以持己。则不期威而自威。夫所谓脩身检身诚身。皆所以求在我者。
公子荆善居室。比之进学工夫。有循序不躐之意。其所谓始有者。志道以立其基也。其所谓少有者。据德而守其本也。其所谓富有者。依仁以全其体也。其所谓苟有者。学不及望未见之意也。夫子借其居室之善。而喻后人造道入学之节次阶级。俾勿以隙光瞥见自大而自夸。学之而不倦。为之而不厌。有如公子荆之有其室也。大圣人片言只辞。莫不有至理存焉。
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此与大舜三年成邑。三年成都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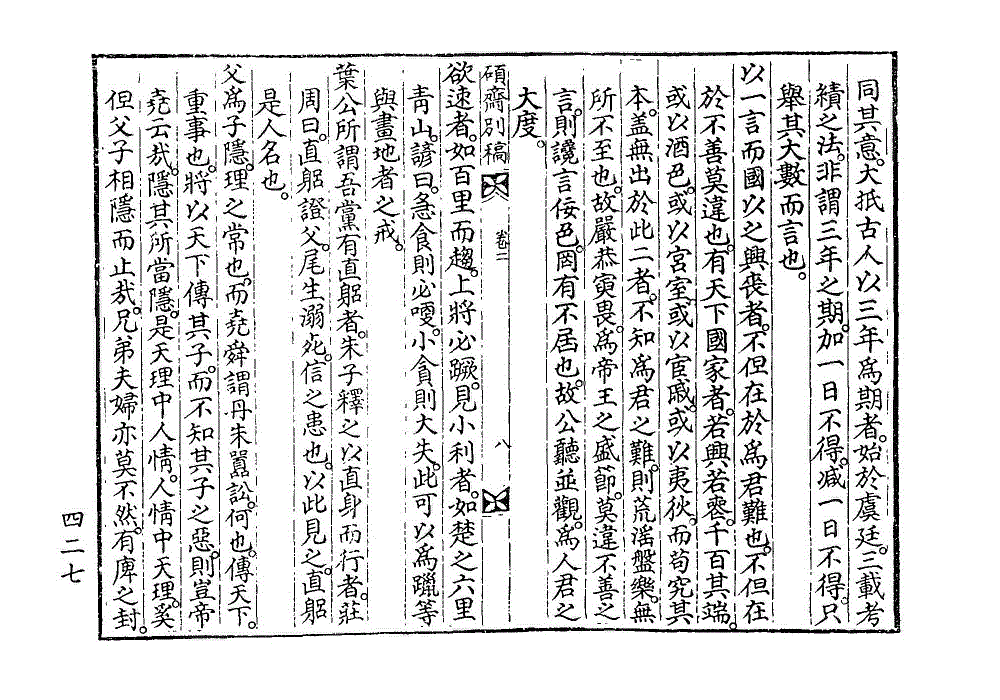 同其意。大抵古人以三年为期者。始于虞廷。三载考绩之法。非谓三年之期。加一日不得。减一日不得。只举其大数而言也。
同其意。大抵古人以三年为期者。始于虞廷。三载考绩之法。非谓三年之期。加一日不得。减一日不得。只举其大数而言也。以一言而国以之兴丧者。不但在于为君难也。不但在于不善莫违也。有天下国家者。若兴若丧。千百其端。或以酒色。或以宫室。或以宦戚。或以夷狄。而苟究其本。盖无出于此二者。不知为君之难。则荒淫盘乐。无所不至也。故严恭寅畏。为帝王之盛节。莫违不善之言。则谗言佞色。罔有不届也。故公听并观。为人君之大度。
欲速者。如百里而趋。上将必蹶。见小利者。如楚之六里青山。谚曰。急食则必哽。小贪则大失。此可以为躐等与画地者之戒。
叶公所谓吾党有直躬者。朱子释之以直身而行者。庄周曰。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以此见之。直躬是人名也。
父为子隐。理之常也。而尧舜谓丹朱嚣讼。何也。传天下。重事也。将以天下传其子。而不知其子之恶。则岂帝尧云哉。隐其所当隐。是天理中人情。人情中天理。奚但父子相隐而止哉。兄弟夫妇亦莫不然。有庳之封。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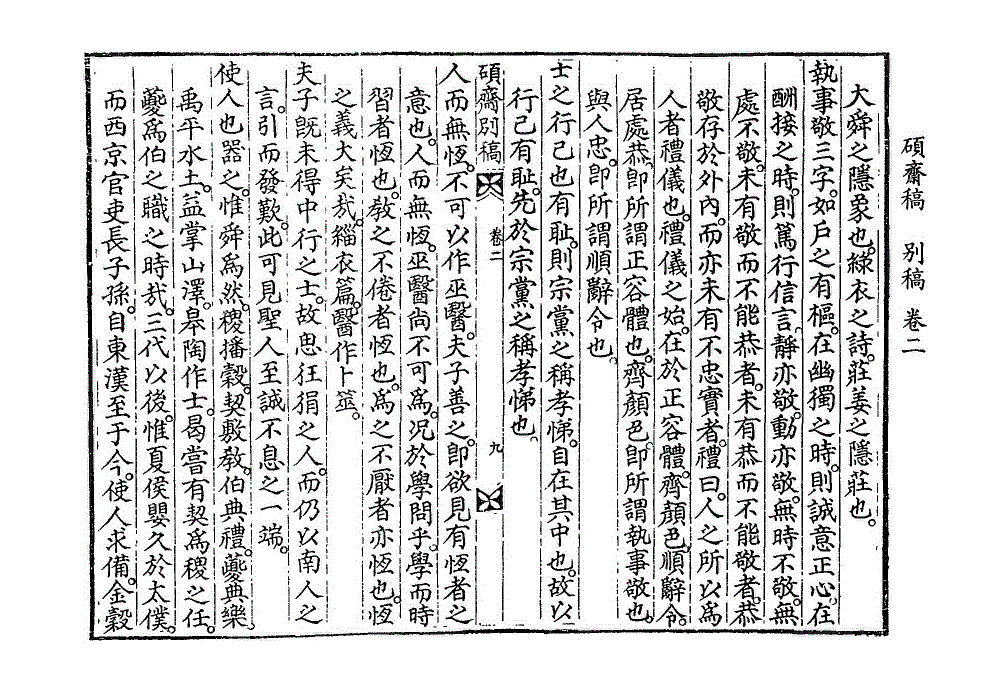 大舜之隐象也。绿衣之诗。庄姜之隐庄也。
大舜之隐象也。绿衣之诗。庄姜之隐庄也。执事敬三字。如户之有枢。在幽独之时。则诚意正心。在酬接之时。则笃行信言。静亦敬。动亦敬。无时不敬。无处不敬。未有敬而不能恭者。未有恭而不能敬者。恭敬存于外内。而亦未有不忠实者。礼曰。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居处恭。即所谓正容体也。齐颜色。即所谓执事敬也。与人忠。即所谓顺辞令也。
士之行己也有耻。则宗党之称孝悌。自在其中也。故以行己有耻。先于宗党之称孝悌也。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夫子善之。即欲见有恒者之意也。人而无恒。巫医尚不可为。况于学问乎。学而时习者恒也。教之不倦者恒也。为之不厌者亦恒也。恒之义大矣哉。缁衣篇。医作卜筮。
夫子既未得中行之士。故思狂狷之人。而仍以南人之言。引而发叹。此可见圣人至诚不息之一端。
使人也器之。惟舜为然。稷播谷。契敷教。伯典礼。夔典乐。禹平水土。益掌山泽。皋陶作士。曷尝有契为稷之任。夔为伯之职之时哉。三代以后。惟夏侯婴久于太仆。而西京官吏长子孙。自东汉至于今。使人求备。金谷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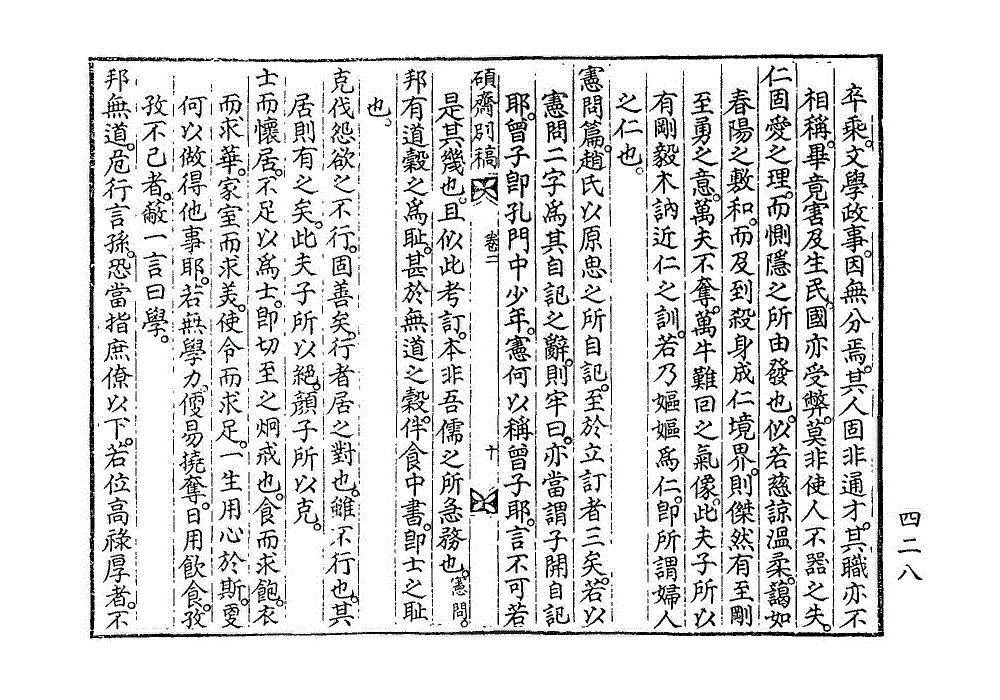 卒乘。文学政事。因无分焉。其人固非通才。其职亦不相称。毕竟害及生民。国亦受弊。莫非使人不器之失。
卒乘。文学政事。因无分焉。其人固非通才。其职亦不相称。毕竟害及生民。国亦受弊。莫非使人不器之失。仁固爱之理。而恻隐之所由发也。似若慈谅温柔。蔼如春阳之敷和。而及到杀身成仁境界。则杰然有至刚至勇之意。万夫不夺。万牛难回之气像。此夫子所以有刚毅木讷近仁之训。若乃妪妪为仁。即所谓妇人之仁也。
宪问篇。赵氏以原思之所自记。至于立订者三矣。若以宪问二字为其自记之辞。则牢曰。亦当谓子开自记耶。曾子即孔门中少年。宪何以称曾子耶。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且似此考订。本非吾儒之所急务也。(宪问。)
邦有道谷之为耻。甚于无道之谷。伴食中书。即士之耻也。
克伐怨欲之不行。固善矣。行者居之对也。虽不行也。其居则有之矣。此夫子所以绝。颜子所以克。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即切至之炯戒也。食而求饱。衣而求华。家室而求美。使令而求足。一生用心于斯。更何以做得他事耶。若无学力。便易挠夺。日用饮食。孜孜不已者。蔽一言曰学。
邦无道。危行言孙。恐当指庶僚以下若位高禄厚者。不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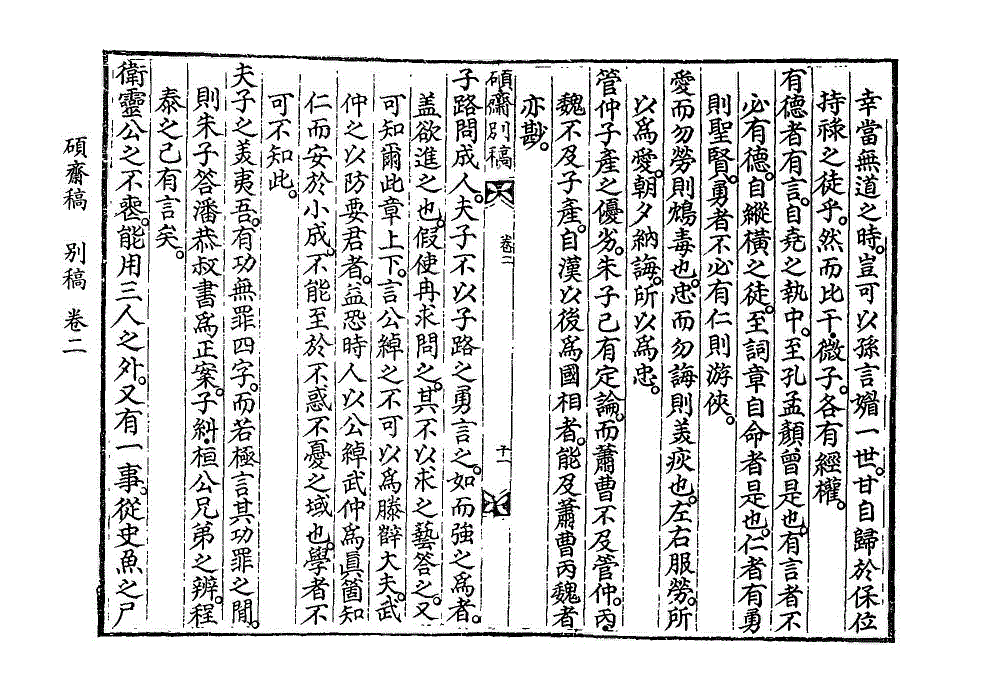 幸当无道之时。岂可以孙言媚一世。甘自归于保位持禄之徒乎。然而比干,微子。各有经权。
幸当无道之时。岂可以孙言媚一世。甘自归于保位持禄之徒乎。然而比干,微子。各有经权。有德者有言。自尧之执中。至孔孟颜曾是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自纵横之徒。至词章自命者是也。仁者有勇则圣贤。勇者不必有仁则游侠。
爱而勿劳则鸩毒也。忠而勿诲则美疢也。左右服劳。所以为爱。朝夕纳诲。所以为忠。
管仲子产之优劣。朱子已有定论。而萧曹不及管仲。丙,魏不及子产。自汉以后为国相者。能及萧曹丙魏者亦鲜。
子路问成人。夫子不以子路之勇言之。如而强之为者。盖欲进之也。假使冉求问之。其不以求之艺答之。又可知尔此章上下。言公绰之不可以为滕辥大夫。武仲之以防要君者。益恐时人以公绰武仲为真个知仁而安于小成。不能至于不惑不忧之域也。学者不可不知此。
夫子之美夷吾。有功无罪四字。而若极言其功罪之閒。则朱子答潘恭叔书为正案。子纠,桓公兄弟之辨。程泰之已有言矣。
卫灵公之不丧。能用三人之外。又有一事。从史鱼之尸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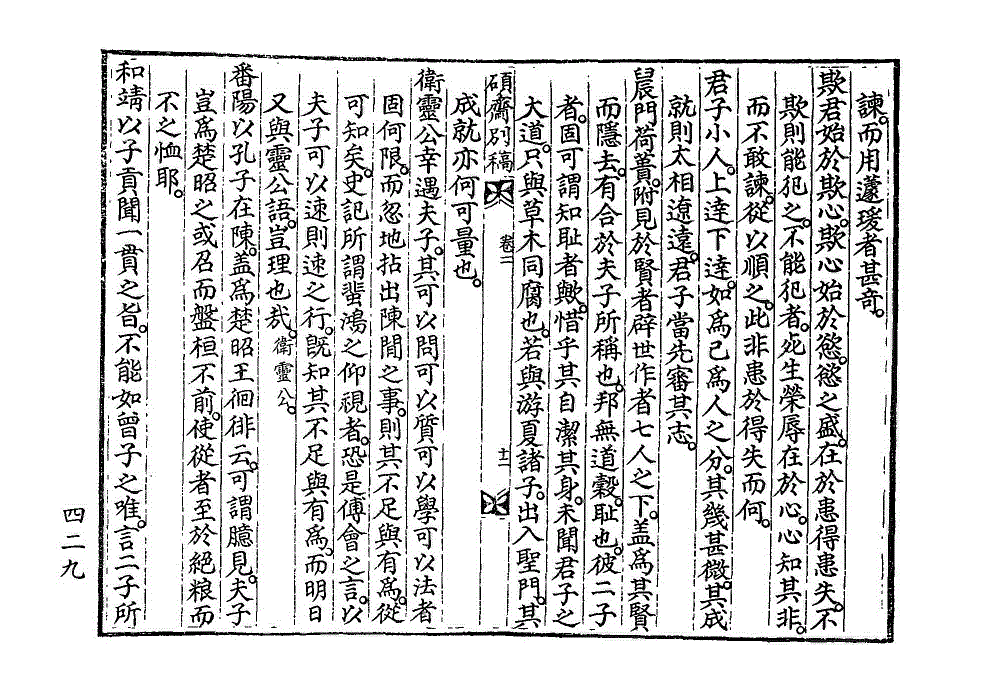 谏。而用蘧瑗者甚奇。
谏。而用蘧瑗者甚奇。欺君始于欺心。欺心始于欲。欲之盛。在于患得患失。不欺则能犯之。不能犯者。死生荣辱在于心。心知其非。而不敢谏。从以顺之。此非患于得失而何。
君子小人。上达下达。如为己为人之分。其几甚微。其成就则太相辽远。君子当先审其志。
䢅门荷篑。附见于贤者辟世作者七人之下。盖为其贤而隐去。有合于夫子所称也。邦无道谷。耻也。彼二子者。固可谓知耻者欤。惜乎其自洁其身。未闻君子之大道。只与草木同腐也。若与游夏诸子。出入圣门。其成就亦何可量也。
卫灵公幸遇夫子。其可以问可以质可以学可以法者固何限。而忽地拈出陈閒之事。则其不足与有为。从可知矣。史记所谓蜚鸿之仰视者。恐是傅会之言。以夫子可以速则速之行。既知其不足与有为。而明日又与灵公语。岂理也哉。(卫灵公。)
番阳以孔子在陈。盖为楚昭王徊徘云。可谓臆见。夫子岂为楚昭之或召而盘桓不前。使从者至于绝粮而不之恤耶。
和靖以子贡闻一贯之旨。不能如曾子之唯。言二子所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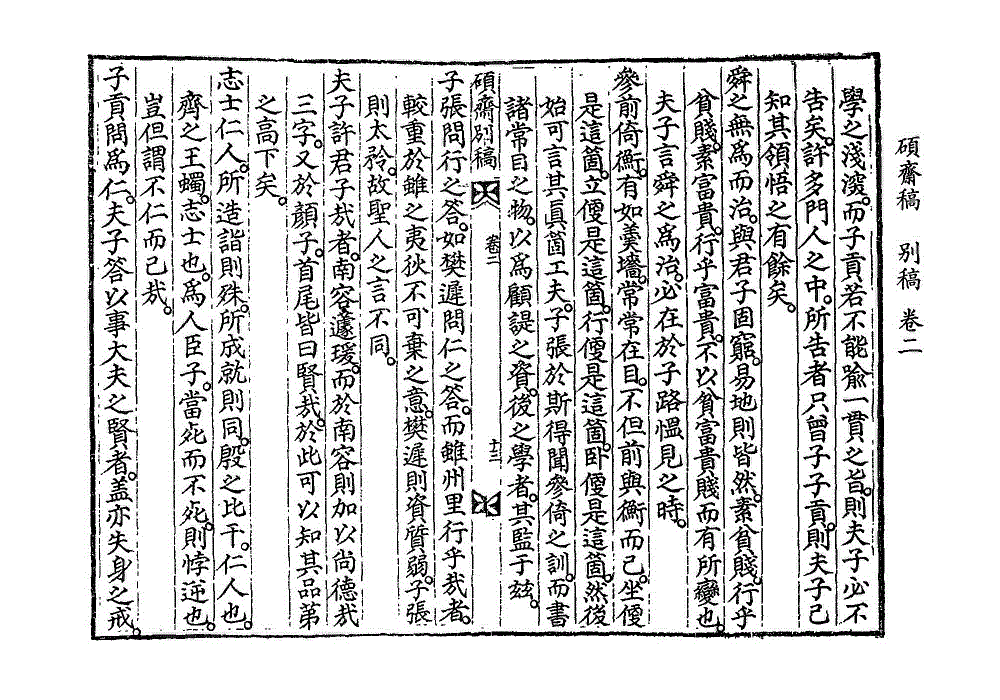 学之浅深。而子贡若不能喻一贯之旨。则夫子必不告矣。许多门人之中。所告者只曾子子贡。则夫子已知其领悟之有馀矣。
学之浅深。而子贡若不能喻一贯之旨。则夫子必不告矣。许多门人之中。所告者只曾子子贡。则夫子已知其领悟之有馀矣。舜之无为而治。与君子固穷。易地则皆然。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不以贫富贵贱而有所变也。夫子言舜之为治。必在于子路愠见之时。
参前倚衡。有如羹墙。常常在目。不但前与衡而已。坐便是这个。立便是这个。行便是这个。卧便是这个。然后始可言其真个工夫。子张于斯得闻参倚之训。而书诸常目之物。以为顾諟之资。后之学者。其监于玆。
子张问行之答。如樊迟问仁之答。而虽州里行乎哉者。较重于虽之夷狄不可弃之意。樊迟则资质弱。子张则太矜。故圣人之言不同。
夫子许君子哉者。南容,蘧瑗。而于南容则加以尚德哉三字。又于颜子。首尾皆曰贤哉。于此可以知其品第之高下矣。
志士仁人。所造诣则殊。所成就则同。殷之比干。仁人也。齐之王蠋。志士也。为人臣子。当死而不死。则悖逆也。岂但谓不仁而已哉。
子贡问为仁。夫子答以事大夫之贤者。盖亦失身之戒。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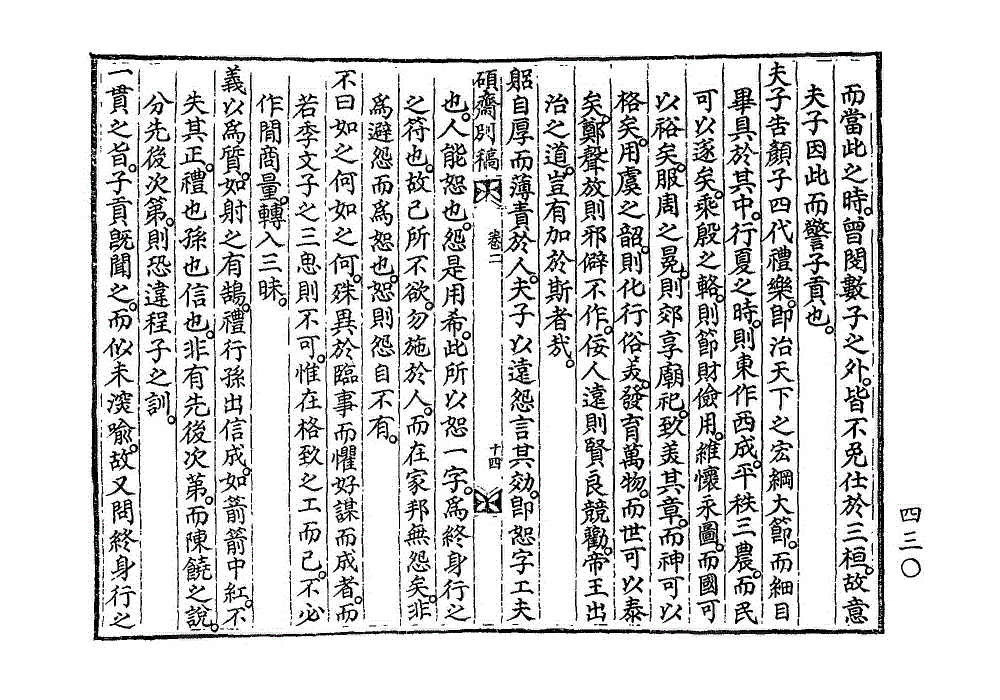 而当此之时。曾闵数子之外。皆不免仕于三桓。故意夫子因此而警子贡也。
而当此之时。曾闵数子之外。皆不免仕于三桓。故意夫子因此而警子贡也。夫子告颜子四代礼乐。即治天下之宏纲大节。而细目毕具于其中。行夏之时。则东作西成。平秩三农。而民可以遂矣。乘殷之辂。则节财俭用。维怀永图。而国可以裕矣。服周之冕。则郊享庙祀。致美其章。而神可以格矣。用虞之韶。则化行俗美。发育万物。而世可以泰矣。郑声放则邪僻不作。佞人远则贤良竞劝。帝王出治之道。岂有加于斯者哉。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夫子以远怨言其效。即恕字工夫也。人能恕也。怨是用希。此所以恕一字。为终身行之之符也。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家邦无怨矣。非为避怨而为恕也。恕则怨自不有。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殊异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而若季文子之三思则不可。惟在格致之工而已。不必作閒商量。转入三昧。
义以为质。如射之有鹄。礼行孙出信成。如箭箭中红。不失其正。礼也孙也信也。非有先后次第。而陈饶之说。分先后次第。则恐违程子之训。
一贯之旨。子贡既闻之。而似未深喻。故又问终身行之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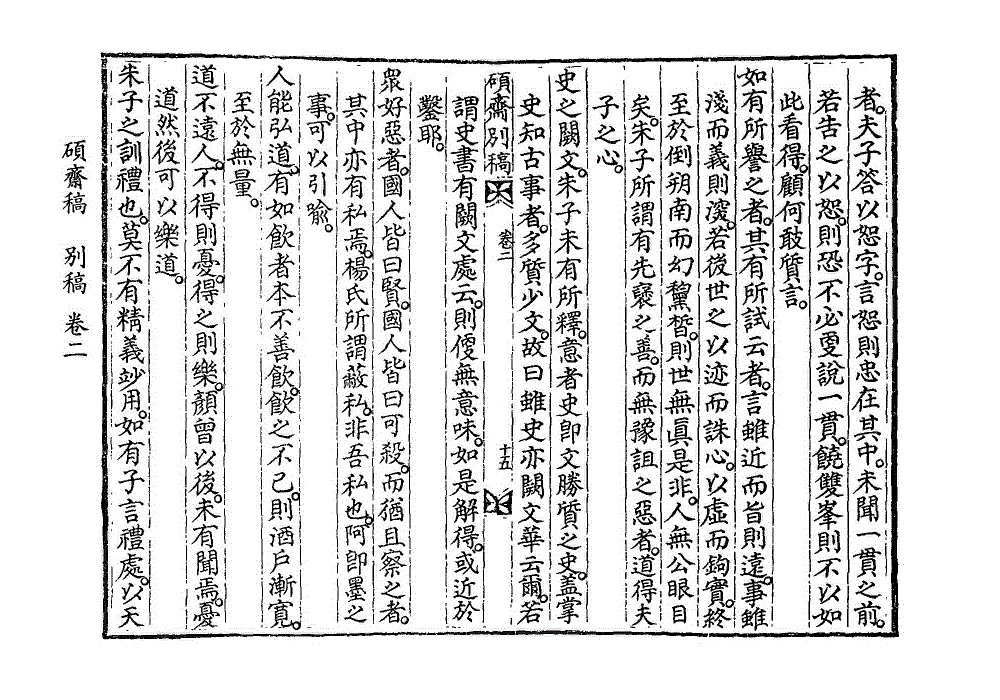 者。夫子答以恕字。言恕则忠在其中。未闻一贯之前。若告之以恕。则恐不必更说一贯。饶双峰则不以如此看得。顾何敢质言。
者。夫子答以恕字。言恕则忠在其中。未闻一贯之前。若告之以恕。则恐不必更说一贯。饶双峰则不以如此看得。顾何敢质言。如有所誉之者。其有所试云者。言虽近而旨则远。事虽浅而义则深。若后世之以迹而诛心。以虚而钩实。终至于倒朔南而幻黧晰。则世无真是非。人无公眼目矣。朱子所谓有先褒之善。而无豫诅之恶者。道得夫子之心。
史之阙文。朱子未有所释。意者史即文胜质之史。盖掌史知古事者。多质少文。故曰虽史亦阙文华云尔。若谓史书有阙文处云。则便无意味。如是解得。或近于凿耶。
众好恶者。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而犹且察之者。其中亦有私焉。杨氏所谓蔽私。非吾私也。阿即墨之事。可以引喻。
人能弘道。有如饮者本不善饮。饮之不已。则酒户渐宽。至于无量。
道不远人。不得则忧。得之则乐。颜曾以后。未有闻焉。忧道然后可以乐道。
朱子之训礼也。莫不有精义妙用。如有子言礼处。以天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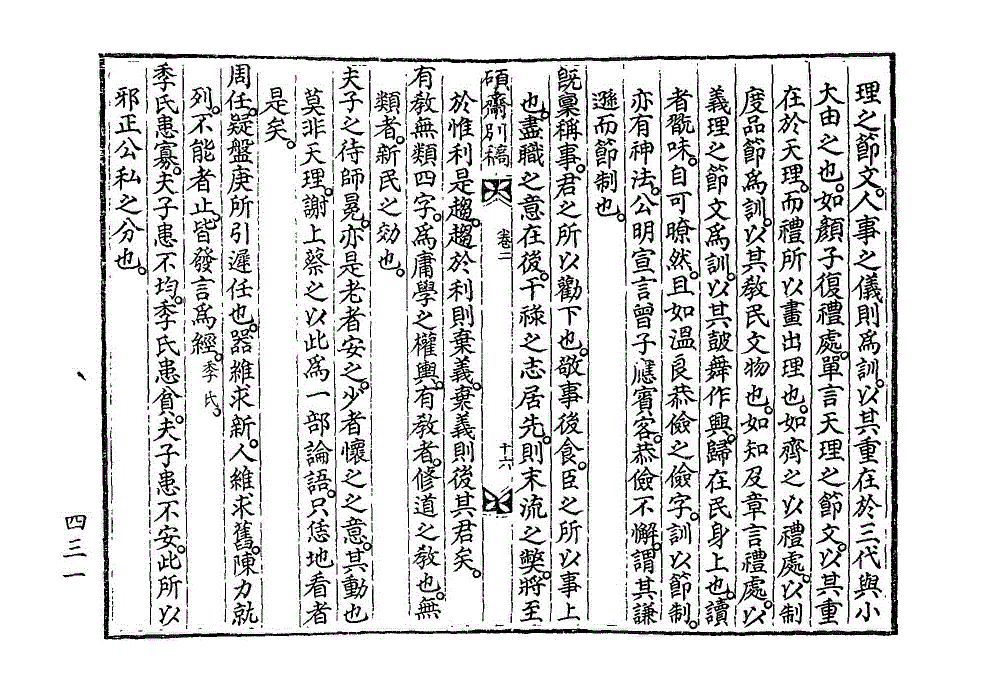 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为训。以其重在于三代与小大由之也。如颜子复礼处。单言天理之节文。以其重在于天理。而礼所以画出理也。如齐之以礼处。以制度品节为训。以其教民文物也。如知及章言礼处。以义理之节文为训。以其鼓舞作兴。归在民身上也。读者玩味。自可暸然。且如温良恭俭之俭字。训以节制。亦有神法。公明宣言曾子应宾客。恭俭不懈。谓其谦逊而节制也。
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为训。以其重在于三代与小大由之也。如颜子复礼处。单言天理之节文。以其重在于天理。而礼所以画出理也。如齐之以礼处。以制度品节为训。以其教民文物也。如知及章言礼处。以义理之节文为训。以其鼓舞作兴。归在民身上也。读者玩味。自可暸然。且如温良恭俭之俭字。训以节制。亦有神法。公明宣言曾子应宾客。恭俭不懈。谓其谦逊而节制也。既禀称事。君之所以劝下也。敬事后食。臣之所以事上也。尽职之意在后。干禄之志居先。则末流之弊。将至于惟利是趋。趋于利则弃义。弃义则后其君矣。
有教无类四字。为庸学之权舆。有教者。修道之教也。无类者。新民之效也。
夫子之待师冕。亦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其动也莫非天理。谢上蔡之以此为一部论语。只恁地看者是矣。
周任。疑盘庚所引迟任也。器维求新。人维求旧。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皆发言为经。(季氏。)
季氏患寡。夫子患不均。季氏患贫。夫子患不安。此所以邪正公私之分也。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2H 页
 季氏将代颛臾。夫子严责由求。仍言礼乐征伐之所自出。陪臣之执国命。其警之也切。而辟之也廓。以此观之。颛臾下二章。恐在同时。
季氏将代颛臾。夫子严责由求。仍言礼乐征伐之所自出。陪臣之执国命。其警之也切。而辟之也廓。以此观之。颛臾下二章。恐在同时。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舜之于苗也。苗顽不格。尚用干舞。况邦内附庸之颛臾乎。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即指中人以下言也。若上等人则如互乡童子。皆可以化之。中人以下。专靠友辅之功。设如人人者皆求益友。则便辟善柔者。将无改过迁善之路矣。此所以举善教不能。为在上者之化矣。陈忠肃曰。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皆以第一段为重。礼乐能节之。则可以立于礼成于乐矣。骄乐能节之。则可以恭于人久于约矣。
君子三戒。以秦始,汉武之事订之。则节节相合。盖不能制人心而致此也。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言。言其敬也。言畏而不言敬者。尤警切。殷汤之顾諟。是圣敬日跻之本。
九思皆统于一心。而心有出入。故辄思所以得其宜之方。其中事思敬。所包者广。事天事亲事君事长之事。此事彼事一事二事之事。皆由于敬。其馀八思则各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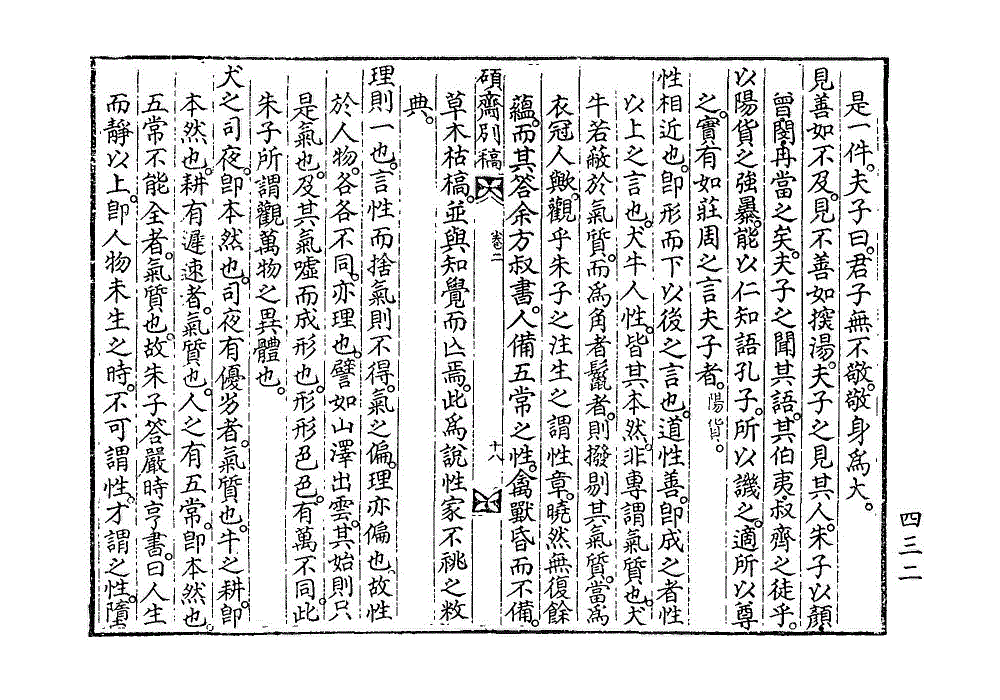 是一件。夫子曰。君子无不敬。敬身为大。
是一件。夫子曰。君子无不敬。敬身为大。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夫子之见其人。朱子以颜,曾,闵,冉当之矣。夫子之闻其语。其伯夷,叔齐之徒乎。
以阳货之强㬥。能以仁知语孔子。所以讥之。适所以尊之。实有如庄周之言夫子者。(阳货。)
性相近也。即形而下以后之言也。道性善。即成之者性以上之言也。犬牛人性。皆其本然。非专谓气质也。犬牛若蔽于气质。而为角者鬣者。则拨剔其气质。当为衣冠人欤。观乎朱子之注生之谓性章。晓然无复馀蕴。而其答余方叔书。人备五常之性。禽兽昏而不备。草木枯槁。并与知觉而亡焉。此为说性家不祧之敉典。
理则一也。言性而舍气则不得。气之偏。理亦偏也。故性于人物。各各不同。亦理也。譬如山泽出云。其始则只是气也。及其气嘘而成形也。形形色色。有万不同。此朱子所谓观万物之异体也。
犬之司夜。即本然也。司夜有优劣者。气质也。牛之耕。即本然也。耕有迟速者。气质也。人之有五常。即本然也。五常不能全者。气质也。故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以上。即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性。才谓之性。堕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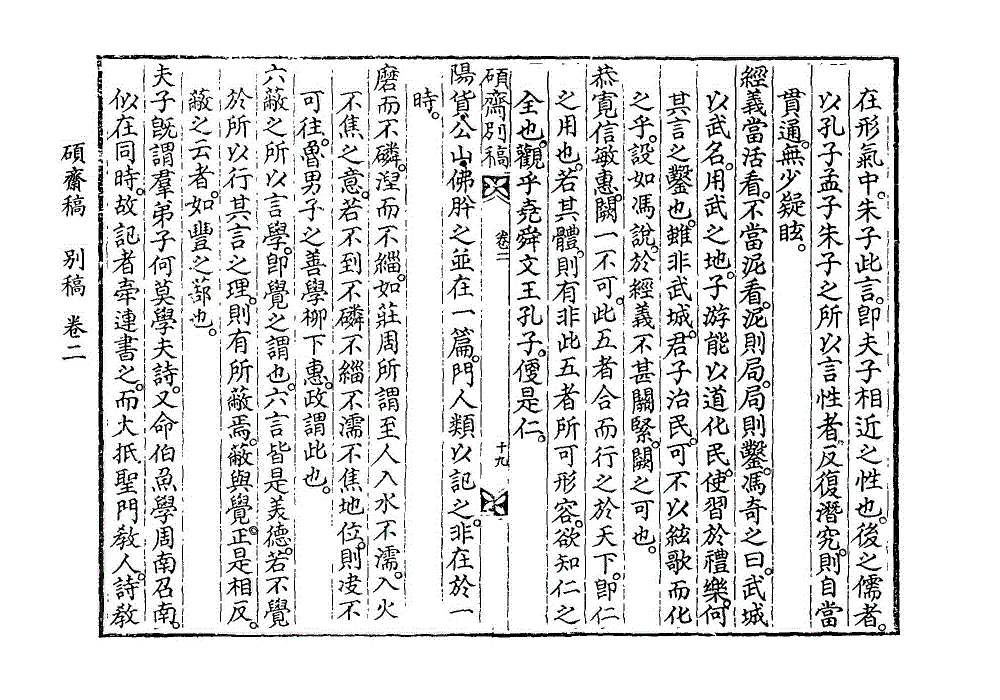 在形气中。朱子此言。即夫子相近之性也。后之儒者。以孔子孟子朱子之所以言性者。反复潜究。则自当贯通。无少疑眩。
在形气中。朱子此言。即夫子相近之性也。后之儒者。以孔子孟子朱子之所以言性者。反复潜究。则自当贯通。无少疑眩。经义当活看。不当泥看。泥则局。局则凿。冯奇之曰。武城以武名。用武之地。子游能以道化民。使习于礼乐。何其言之凿也。虽非武城。君子治民。可不以弦歌而化之乎。设如冯说。于经义不甚关紧。阙之可也。
恭宽信敏惠。阙一不可。此五者合而行之于天下。即仁之用也。若其体。则有非此五者所可形容。欲知仁之全也。观乎尧舜文王孔子。便是仁。
阳货,公山,佛肸之并在一篇。门人类以记之。非在于一时。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如庄周所谓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之意。若不到不磷不缁不濡不焦地位。则决不可往。鲁男子之善学柳下惠。政谓此也。
六蔽之所以言学。即觉之谓也。六言皆是美德。若不觉于所以行其言之理。则有所蔽焉。蔽与觉。正是相反。蔽之云者。如丰之蔀也。
夫子既谓群弟子何莫学夫诗。又命伯鱼学周南召南。似在同时。故记者牵连书之。而大抵圣门教人。诗教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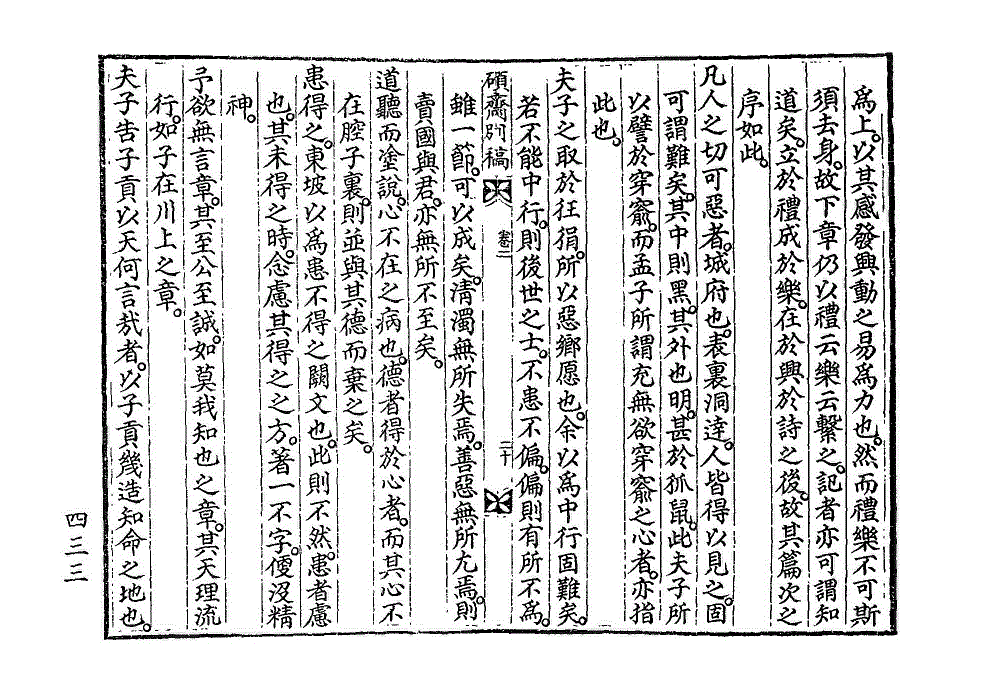 为上。以其感发兴动之易为力也。然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下章仍以礼云乐云系之。记者亦可谓知道矣。立于礼成于乐。在于兴于诗之后。故其篇次之序如此。
为上。以其感发兴动之易为力也。然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下章仍以礼云乐云系之。记者亦可谓知道矣。立于礼成于乐。在于兴于诗之后。故其篇次之序如此。凡人之切可恶者。城府也。表里洞达。人皆得以见之。固可谓难矣。其中则黑。其外也明。甚于狐鼠。此夫子所以譬于穿窬。而孟子所谓充无欲穿窬之心者。亦指此也。
夫子之取于狂狷。所以恶乡愿也。余以为中行固难矣。若不能中行。则后世之士。不患不偏。偏则有所不为。虽一节。可以成矣。清浊无所失焉。善恶无所尤焉。则卖国与君。亦无所不至矣。
道听而涂说。心不在之病也。德者得于心者。而其心不在腔子里。则并与其德而弃之矣。
患得之。东坡以为患不得之阙文也。此则不然。患者虑也。其未得之时。念虑其得之之方。著一不字。便没精神。
予欲无言章。其至公至诚。如莫我知也之章。其天理流行。如子在川上之章。
夫子告子贡以天何言哉者。以子贡几造知命之地也。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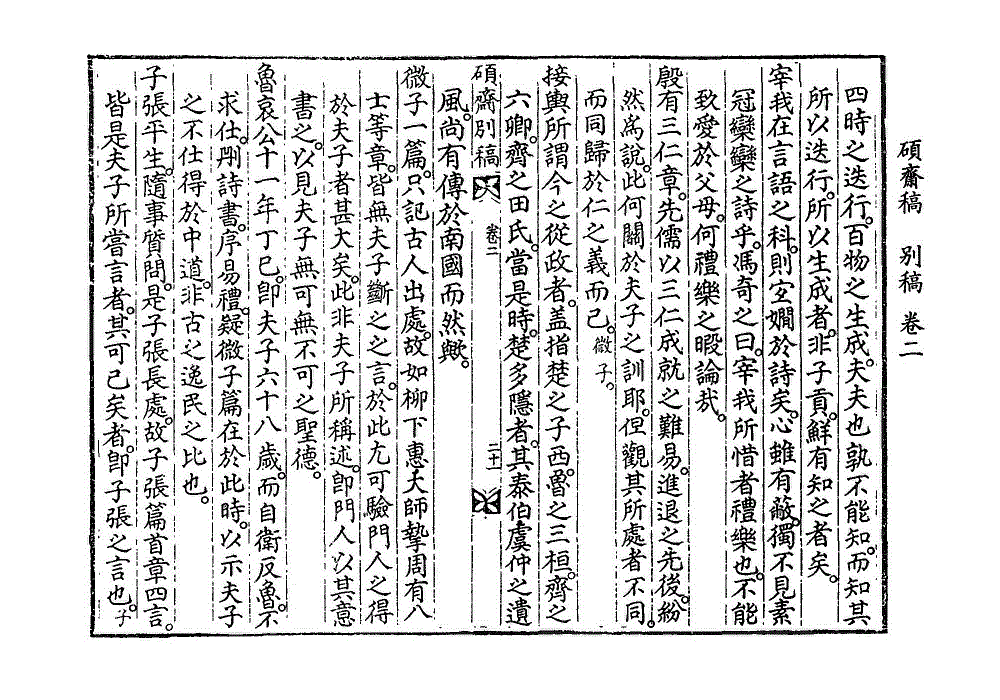 四时之迭行。百物之生成。夫夫也孰不能知。而知其所以迭行。所以生成者。非子贡。鲜有知之者矣。
四时之迭行。百物之生成。夫夫也孰不能知。而知其所以迭行。所以生成者。非子贡。鲜有知之者矣。宰我在言语之科。则宜娴于诗矣。心虽有蔽。独不见素冠栾栾之诗乎。冯奇之曰。宰我所惜者礼乐也。不能致爱于父母。何礼乐之暇论哉。
殷有三仁章。先儒以三仁成就之难易。进退之先后。纷然为说。此何关于夫子之训耶。但观其所处者不同。而同归于仁之义而已。(微子。)
接舆所谓今之从政者。盖指楚之子西。鲁之三桓。齐之六卿。齐之田氏。当是时。楚多隐者。其泰伯,虞仲之遗风。尚有传于南国而然欤。
微子一篇。只记古人出处。故如柳下惠,大师挚周有八士等章。皆无夫子断之之言。于此尤可验门人之得于夫子者甚大矣。此非夫子所称述。即门人以其意书之。以见夫子无可无不可之圣德。
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即夫子六十八岁。而自卫反鲁。不求仕。删诗书。序易礼。疑微子篇在于此时。以示夫子之不仕得于中道。非古之逸民之比也。
子张平生。随事质问。是子张长处。故子张篇首章四言。皆是夫子所尝言者。其可已矣者。即子张之言也。(子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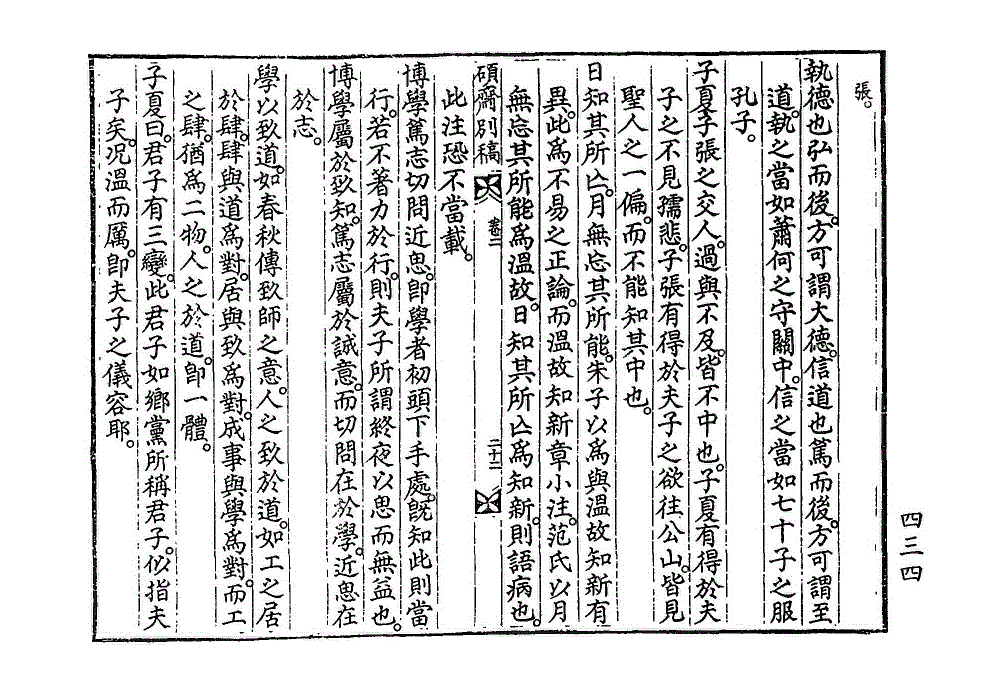 张。)
张。)执德也弘而后。方可谓大德。信道也笃而后。方可谓至道。执之当如萧何之守关中。信之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子夏,子张之交人。过与不及。皆不中也。子夏有得于夫子之不见孺悲。子张有得于夫子之欲往公山。皆见圣人之一偏。而不能知其中也。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朱子以为与温故知新有异。此为不易之正论。而温故知新章小注。范氏以月无忘其所能为温故。日知其所亡为知新。则语病也。此注恐不当载。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即学者初头下手处。既知此则当行。若不著力于行。则夫子所谓终夜以思而无益也。
博学属于致知。笃志属于诚意。而切问在于学。近思在于志。
学以致道。如春秋传致师之意。人之致于道。如工之居于肆。肆与道为对。居与致为对。成事与学为对。而工之肆。犹为二物。人之于道。即一体。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此君子如乡党所称君子。似指夫子矣。况温而厉。即夫子之仪容耶。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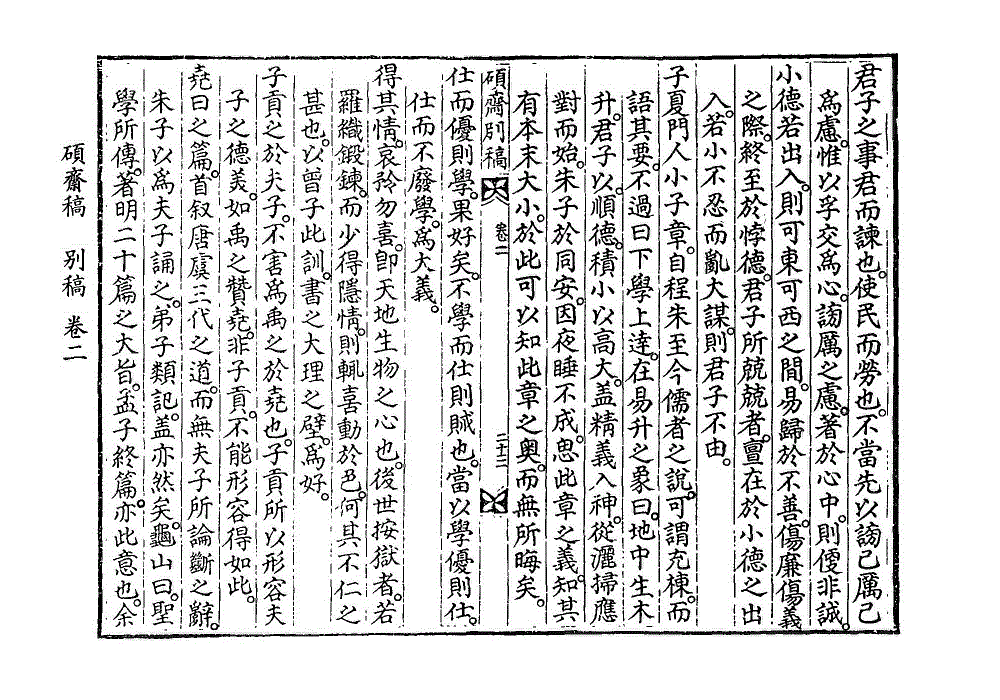 君子之事君而谏也。使民而劳也。不当先以谤己厉己为虑。惟以孚交为心。谤厉之虑。著于心中。则便非诚。
君子之事君而谏也。使民而劳也。不当先以谤己厉己为虑。惟以孚交为心。谤厉之虑。著于心中。则便非诚。小德若出入。则可东可西之间。易归于不善。伤廉伤义之际。终至于悖德。君子所兢兢者。亶在于小德之出入。若小不忍而乱大谋。则君子不由。
子夏门人小子章。自程朱至今儒者之说。可谓充栋。而语其要。不过曰下学上达。在易升之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盖精义入神。从洒扫应对而始。朱子于同安。因夜睡不成。思此章之义。知其有本末大小。于此可以知此章之奥。而无所晦矣。
仕而优则学。果好矣。不学而仕则贼也。当以学优则仕。仕而不废学。为大义。
得其情。哀矜勿喜。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后世按狱者。若罗织锻鍊。而少得隐情。则辄喜动于色。何其不仁之甚也。以曾子此训。书之大理之壁。为好。
子贡之于夫子。不害为禹之于尧也。子贡所以形容夫子之德美。如禹之赞尧。非子贡。不能形容得如此。
尧曰之篇。首叙唐虞三代之道。而无夫子所论断之辞。朱子以为夫子诵之。弟子类记。盖亦然矣。龟山曰。圣学所传。著明二十篇之大旨。孟子终篇。亦此意也。余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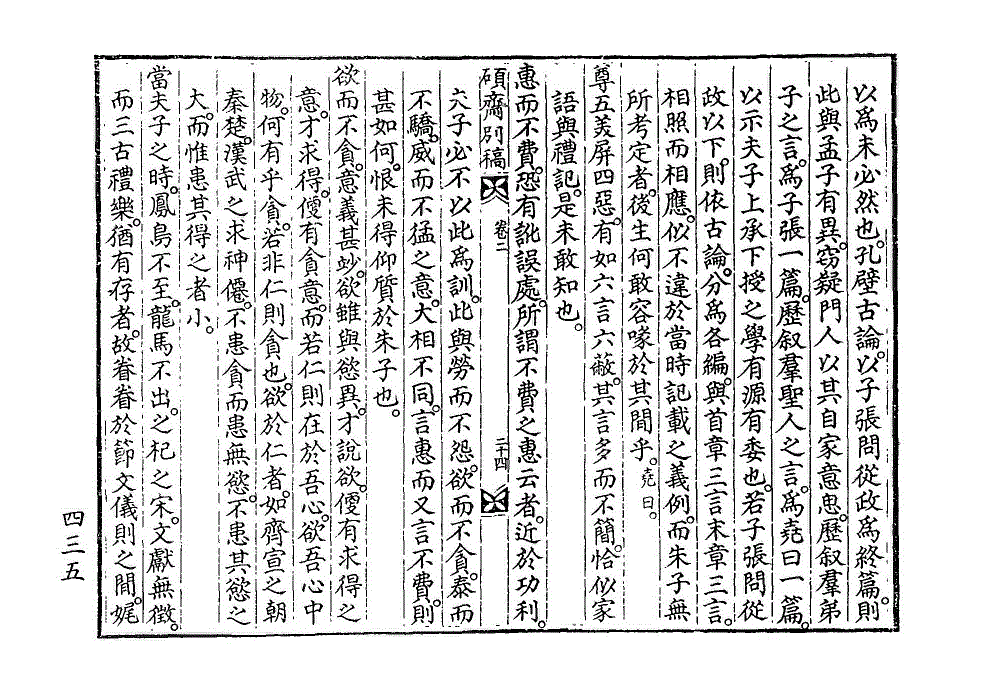 以为未必然也。孔壁古论。以子张问从政为终篇。则此与孟子有异。窃疑门人以其自家意思。历叙群弟子之言。为子张一篇。历叙群圣人之言。为尧曰一篇。以示夫子上承下授之学有源有委也。若子张问从政以下。则依古论分为各编。与首章三言末章三言。相照而相应。似不违于当时记载之义例。而朱子无所考定者。后生何敢容喙于其间乎。(尧曰。)
以为未必然也。孔壁古论。以子张问从政为终篇。则此与孟子有异。窃疑门人以其自家意思。历叙群弟子之言。为子张一篇。历叙群圣人之言。为尧曰一篇。以示夫子上承下授之学有源有委也。若子张问从政以下。则依古论分为各编。与首章三言末章三言。相照而相应。似不违于当时记载之义例。而朱子无所考定者。后生何敢容喙于其间乎。(尧曰。)尊五美屏四恶。有如六言六蔽。其言多而不简。恰似家语与礼记。是未敢知也。
惠而不费。恐有讹误处。所谓不费之惠云者。近于功利。夫子必不以此为训。此与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之意。大相不同。言惠而又言不费。则甚如何。恨未得仰质于朱子也。
欲而不贪。意义甚妙。欲虽与欲异。才说欲。便有求得之意。才求得。便有贪意。而若仁则在于吾心。欲吾心中物。何有乎贪。若非仁则贪也。欲于仁者。如齐宣之朝秦楚。汉武之求神仙。不患贪而患无欲。不患其欲之大。而惟患其得之者小。
当夫子之时。凤鸟不至。龙马不出。之杞之宋。文献无徵。而三古礼乐。犹有存者。故眷眷于节文仪则之间。娓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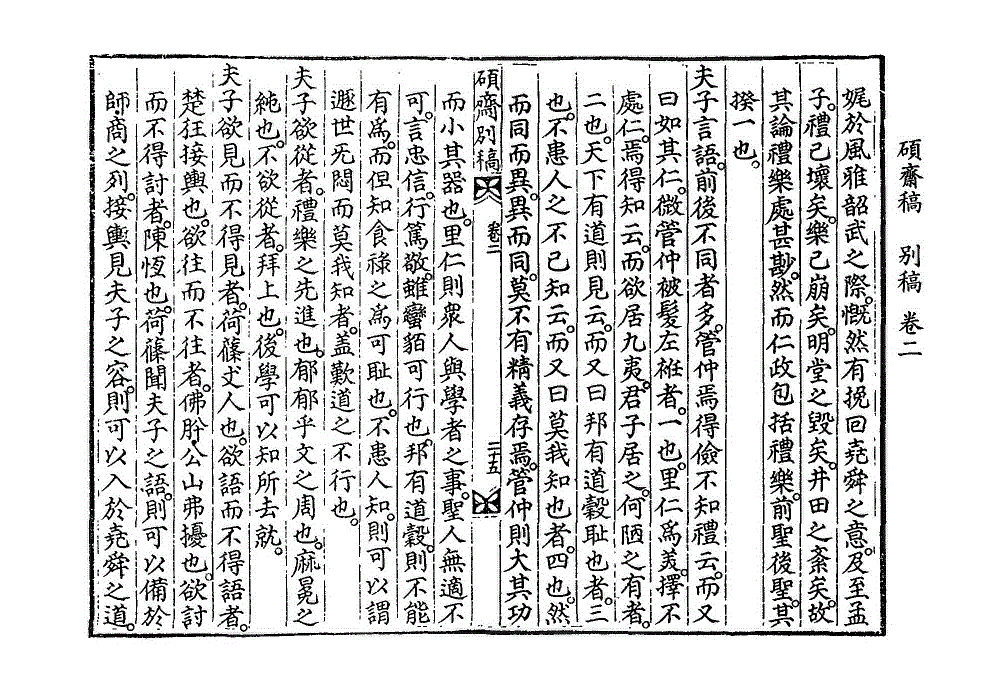 娓于风雅韶武之际。慨然有挽回尧舜之意。及至孟子。礼已坏矣。乐已崩矣。明堂之毁矣。井田之紊矣。故其论礼乐处甚鲜。然而仁政包括礼乐。前圣后圣。其揆一也。
娓于风雅韶武之际。慨然有挽回尧舜之意。及至孟子。礼已坏矣。乐已崩矣。明堂之毁矣。井田之紊矣。故其论礼乐处甚鲜。然而仁政包括礼乐。前圣后圣。其揆一也。夫子言语。前后不同者多。管仲焉得俭不知礼云。而又曰如其仁。微管仲被发左衽者。一也。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云。而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二也。天下有道则见云。而又曰邦有道谷耻也者。三也。不患人之不己知云。而又曰莫我知也者。四也。然而同而异。异而同。莫不有精义存焉。管仲则大其功而小其器也。里仁则众人与学者之事。圣人无适不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可行也。邦有道谷。则不能有为。而但知食禄之为可耻也。不患人知。则可以谓遁世无闷而莫我知者。盖叹道之不行也。
夫子欲从者。礼乐之先进也。郁郁乎文之周也。麻冕之纯也。不欲从者。拜上也。后学可以知所去就。
夫子欲见而不得见者。荷蓧丈人也。欲语而不得语者。楚狂接舆也。欲往而不往者。佛肸,公山弗扰也。欲讨而不得讨者。陈恒也。荷蓧闻夫子之语。则可以备于师,商之列。接舆见夫子之容。则可以入于尧舜之道。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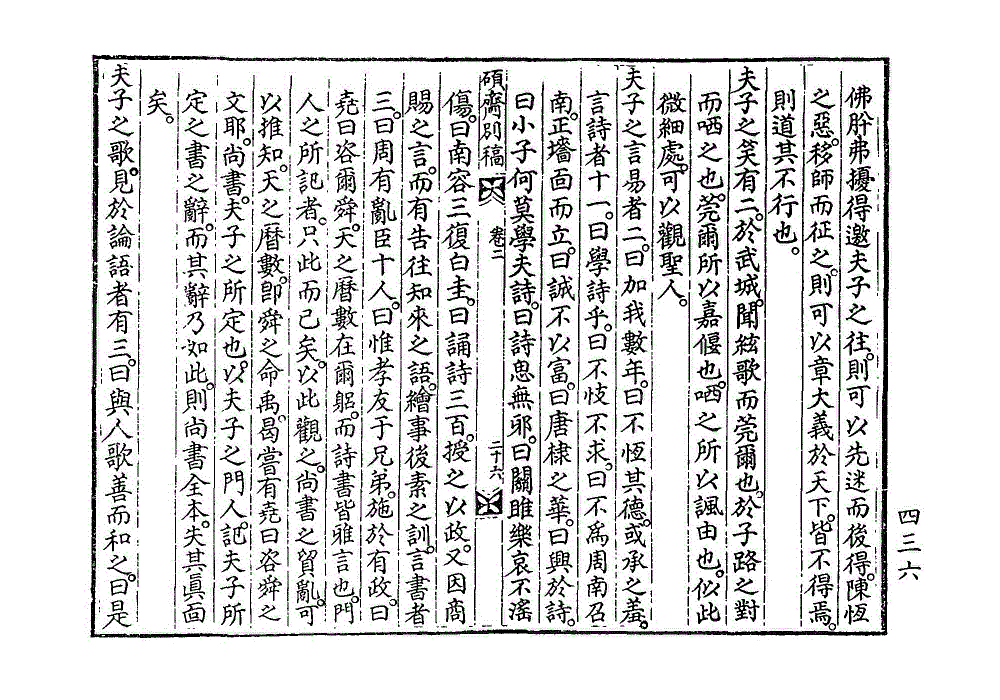 佛肸弗扰得邀夫子之往。则可以先迷而后得。陈恒之恶。移师而征之。则可以章大义于天下。皆不得焉。则道其不行也。
佛肸弗扰得邀夫子之往。则可以先迷而后得。陈恒之恶。移师而征之。则可以章大义于天下。皆不得焉。则道其不行也。夫子之笑有二。于武城。闻弦歌而莞尔也。于子路之对而哂之也。莞尔所以嘉偃也。哂之所以讽由也。似此微细处。可以观圣人。
夫子之言易者二。曰加我数年。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诗者十一。曰学诗乎。曰不忮不求。曰不为周南召南。正墙面而立。曰诚不以富。曰唐棣之华。曰兴于诗。曰小子何莫学夫诗。曰诗思无邪。曰关雎乐哀不淫伤。曰南容三复白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又因商赐之言。而有告往知来之语。绘事后素之训。言书者三。曰周有乱臣十人。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而诗书皆雅言也。门人之所记者。只此而已矣。以此观之。尚书之贸乱。可以推知。天之历数。即舜之命禹。曷尝有尧曰咨舜之文耶。尚书。夫子之所定也。以夫子之门人。记夫子所定之书之辞。而其辞乃如此。则尚书全本。失其真面矣。
夫子之歌。见于论语者有三。曰与人歌善而和之。曰是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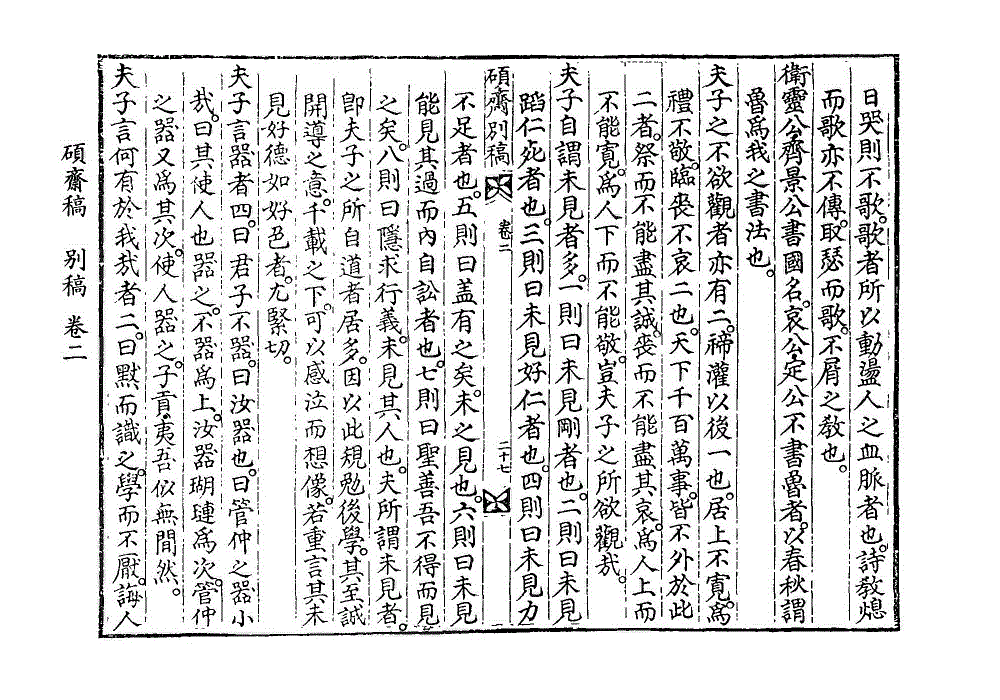 日哭则不歌。歌者所以动荡人之血脉者也。诗教熄而歌亦不传。取瑟而歌。不屑之教也。
日哭则不歌。歌者所以动荡人之血脉者也。诗教熄而歌亦不传。取瑟而歌。不屑之教也。卫灵公,齐景公书国名。哀公,定公不书鲁者。以春秋谓鲁为我之书法也。
夫子之不欲观者亦有二。禘灌以后一也。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二也。天下千百万事。皆不外于此二者。祭而不能尽其诚。丧而不能尽其哀。为人上而不能宽。为人下而不能敬。岂夫子之所欲观哉。
夫子自谓未见者多。一则曰未见刚者也。二则曰未见蹈仁死者也。三则曰未见好仁者也。四则曰未见力不足者也。五则曰盖有之矣。未之见也。六则曰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七则曰圣善吾不得而见之矣。八则曰隐求行义。未见其人也。夫所谓未见者。即夫子之所自道者居多。因以此规勉后学。其至诚开导之意。千载之下。可以感泣而想像。若重言其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尤紧切。
夫子言器者四。曰君子不器。曰汝器也。曰管仲之器小哉。曰其使人也器之。不器为上。汝器瑚琏为次。管仲之器又为其次。使人器之。子贡,夷吾似无间然。
夫子言何有于我哉者二。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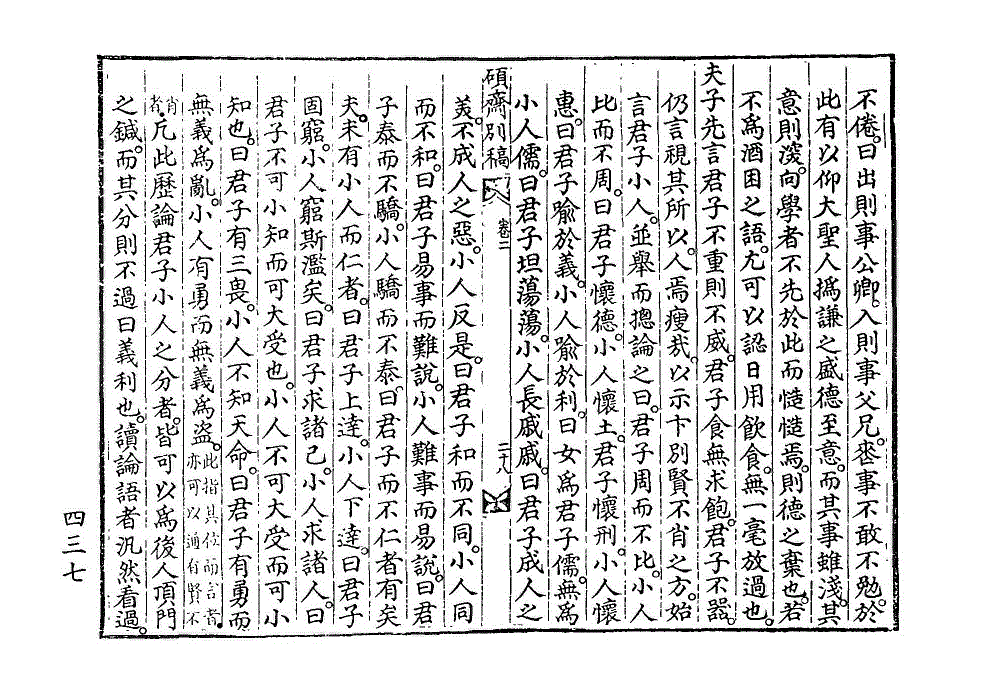 不倦。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于此有以仰大圣人撝谦之盛德至意。而其事虽浅。其意则深。向学者不先于此而慥慥焉。则德之弃也。若不为酒困之语。尤可以认日用饮食。无一毫放过也。
不倦。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于此有以仰大圣人撝谦之盛德至意。而其事虽浅。其意则深。向学者不先于此而慥慥焉。则德之弃也。若不为酒困之语。尤可以认日用饮食。无一毫放过也。夫子先言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食无求饱。君子不器。仍言视其所以。人焉瘦哉。以示卞别贤不肖之方。始言君子小人。并举而总论之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君子易事而难说。小人难事而易说。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曰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此指其位而言者。亦可以通有贤不肖者。)凡此历论君子小人之分者。皆可以为后人顶门之针。而其分则不过曰义利也。读论语者汎然看过。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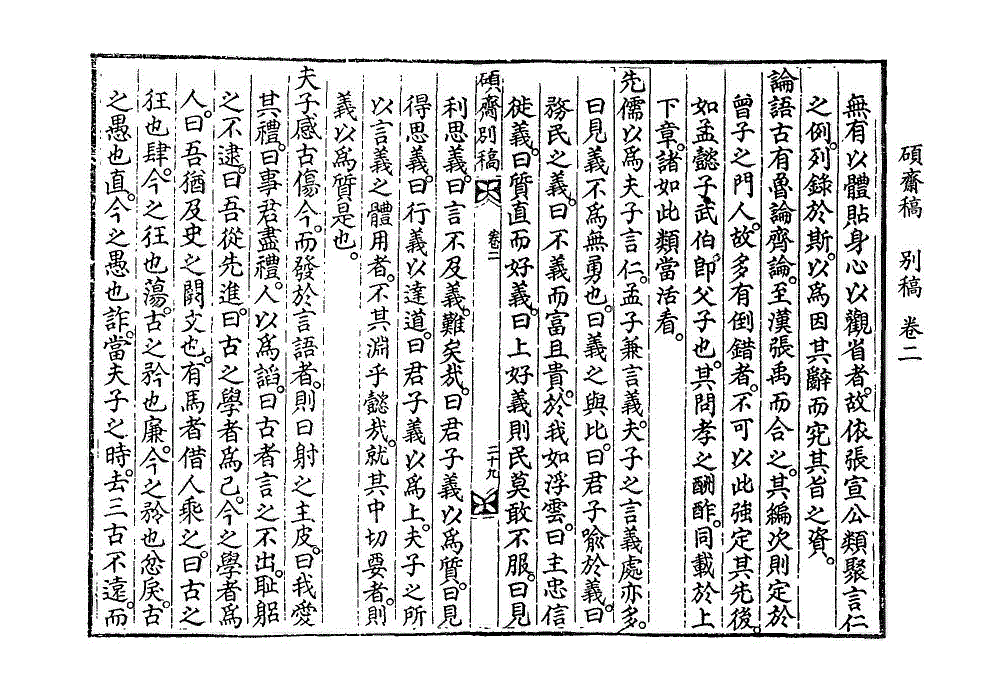 无有以体贴身心以观省者。故依张宣公类聚言仁之例。列录于斯。以为因其辞而究其旨之资。
无有以体贴身心以观省者。故依张宣公类聚言仁之例。列录于斯。以为因其辞而究其旨之资。论语古有鲁论齐论。至汉张禹而合之。其编次则定于曾子之门人。故多有倒错者。不可以此强定其先后。如孟懿子,武伯。即父子也。其问孝之酬酢。同载于上下章。诸如此类当活看。
先儒以为夫子言仁。孟子兼言义。夫子之言义处亦多。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曰义之与比。曰君子喻于义。曰务民之义。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曰主忠信徙义。曰质直而好义。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曰见利思义。曰言不及义。难矣哉。曰君子义以为质。曰见得思义。曰行义以达道。曰君子义以为上。夫子之所以言义之体用者。不其渊乎懿哉。就其中切要者。则义以为质是也。
夫子感古伤今。而发于言语者。则曰射之主皮。曰我爱其礼。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曰吾从先进。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当夫子之时。去三古不远。而
硕斋别稿卷之二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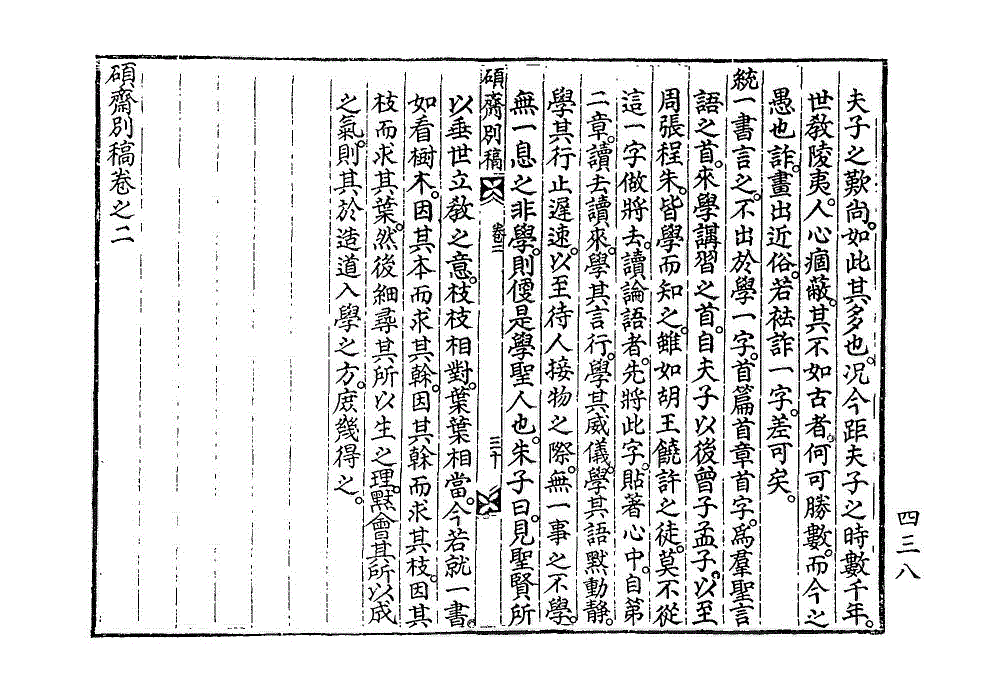 夫子之叹尚。如此其多也。况今距夫子之时数千年。世教陵夷。人心痼蔽。其不如古者。何可胜数。而今之愚也诈。画出近俗。若袪诈一字。差可矣。
夫子之叹尚。如此其多也。况今距夫子之时数千年。世教陵夷。人心痼蔽。其不如古者。何可胜数。而今之愚也诈。画出近俗。若袪诈一字。差可矣。统一书言之。不出于学一字。首篇首章首字。为群圣言语之首。来学讲习之首。自夫子以后曾子孟子。以至周张程朱。皆学而知之。虽如胡王饶许之徒。莫不从这一字做将去。读论语者。先将此字。贴著心中。自第二章。读去读来。学其言行。学其威仪。学其语默动静。学其行止迟速。以至待人接物之际。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息之非学。则便是学圣人也。朱子曰。见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今若就一书。如看树木。因其本而求其干。因其干而求其枝。因其枝而求其叶。然后细寻其所以生之理。默会其所以成之气。则其于造道入学之方。庶几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