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x 页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二)
辨
辨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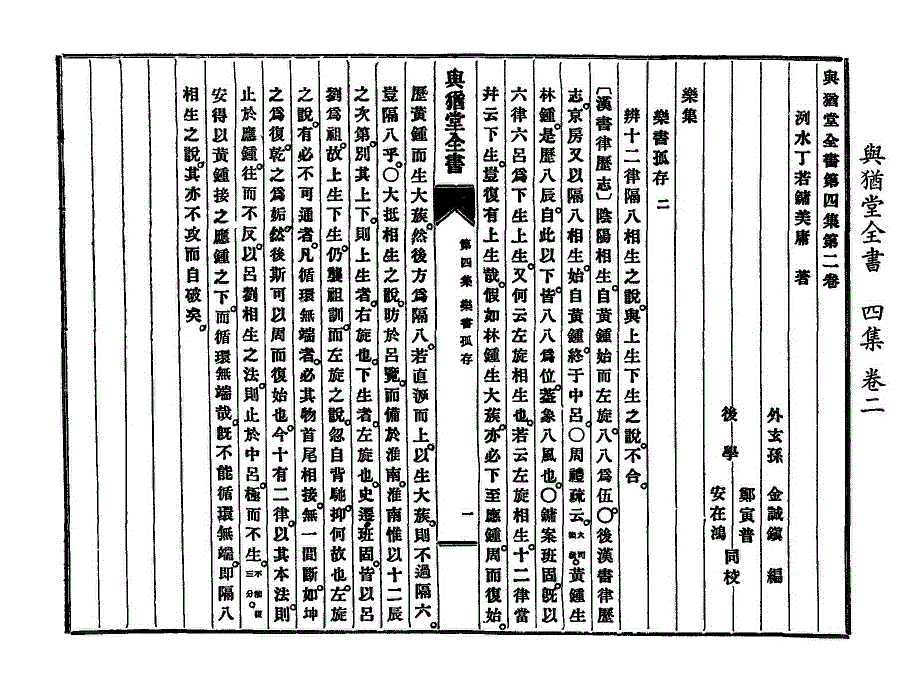 辨十二律隔八相生之说。与上生下生之说。不合。
辨十二律隔八相生之说。与上生下生之说。不合。《汉书律历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〇后汉书律历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始自黄钟。终于中吕。〇周礼疏云。(大司乐疏。)黄钟生林钟。是历八辰。自此以下。皆八八为位。盖象八风也。〇镛案班固。既以六律六吕为下生上生。又何云左旋相生也。若云左旋相生。十二律当并云下生。岂复有上生哉。假如林钟生大蔟。亦必下至应钟。周而复始。历黄钟而生大蔟。然后方为隔八。若直溯而上。以生大蔟。则不过隔六。岂隔八乎。〇大抵相生之说。昉于吕览。而备于淮南。淮南惟以十二辰之次第(一作序)。别其上下。则上生者。右旋也。下生者。左旋也。史迁、班固。皆以吕刘为祖。故上生下生。仍袭祖训。而左旋之说。忽自背驰。抑何故也。左旋之说。有必不可通者。凡循环无端者。必其物首尾相接。无一间断。如坤之为复。乾之为姤。然后斯可以周而复始也。今十有二律。以其本法。则止于应钟。往而不反。以吕刘相生之法。则止于中吕。极而不生。(不能复三分。)安得以黄钟接之应钟之下。而循环无端哉。既不能循环无端。即隔八相生之说。其亦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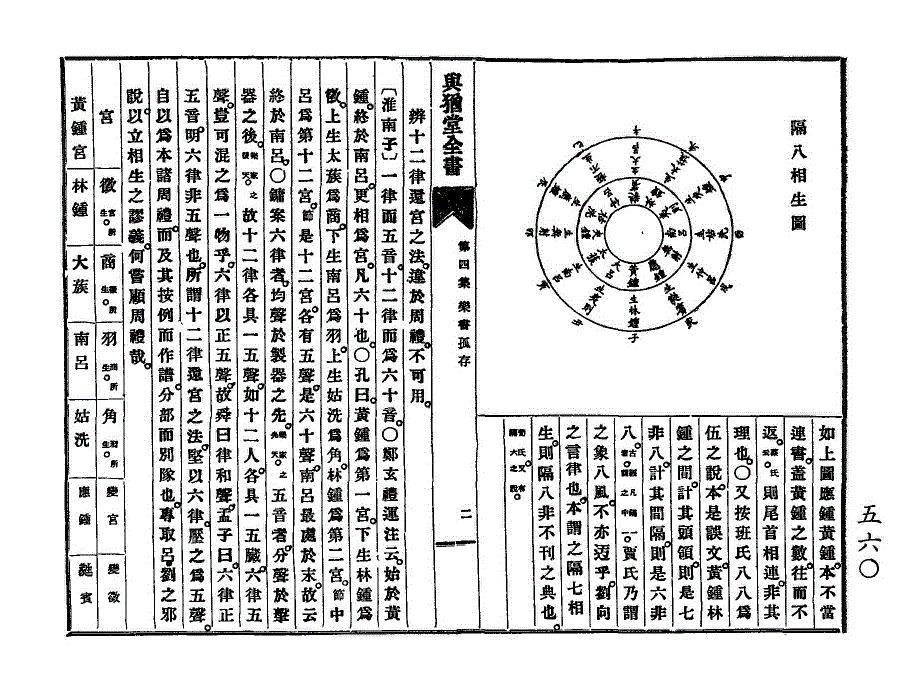 삽화 새창열기
삽화 새창열기如上图应钟黄钟。本不当连书。盖黄钟之数。往而不返。(蔡氏云。)则尾首相连。非其理也。〇又按班氏八八为伍之说。本是误文。黄钟林钟之间。计其头领。则是七非八。计其间隔。则是六非八。(古经凡隔一者。谓之中一。)贾氏乃谓之象八风。不亦迂乎。刘向之言律也。本谓之隔七相生。则隔八非不刊之典也。(荀氏。又有隔六之说。)
辨十二律还宫之法。违于周礼。不可用。
《淮南子》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〇郑玄礼运注云。始于黄钟。终于南吕。更相为宫。凡六十也。〇孔曰。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太蔟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节)中吕为第十二宫。(节)是十二宫。各有五声。是六十声。南吕最处于末。故云终于南吕。〇镛案六律者。均声于制器之先。(乐家之先天。)五音者。分声于击器之后。(乐家之后天。)故十二律各具一五声。如十二人。各具一五脏。六律五声。岂可混之为一物乎。六律以正五声。故舜曰律和声。孟子曰。六律正五音。明六律非五声也。所谓十二律还宫之法。坚以六律。压之为五声。自以为本诸周礼。而及其按例而作谱。分部而别队也。专取吕、刘之邪说。以立相生之谬义。何尝顾周礼哉。
宫徵(宫所生)商(徵所生)羽(商所生)角(羽所生变宫变徵)
黄钟宫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1H 页
 林钟宫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
林钟宫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太蔟宫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
南吕宫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
姑洗宫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
应钟宫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
蕤宾宫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黄钟)
大吕宫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
夷则宫夹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太蔟)
夹钟宫无射中吕黄钟林钟(太蔟南吕)
无射宫中吕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
中吕宫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
周礼未亡。家家有之。请取二至奏乐之文。暂一观之。其有一字半句。与今所谓还宫之法者。毫发近似乎。其文曰。凡乐圜钟为宫。(今应钟。)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何尝云林钟为角。无射为徵。黄钟为羽乎。其文曰。凡乐函钟为宫。(今林钟。)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何尝云应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乎。其文曰。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何尝云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乎。蔡元定。为六十调图。自注曰。以周礼及淮南子礼记注疏。定安在。其以周礼定也。周礼立宫之法。虽不可详。其所云宫角徵羽。乃诸律之五声。非遂以诸律诸吕。压之为五声也。今也以律为声。使应钟为角。而太蔟姑洗以为徵羽。(林钟宫之法。)无射为角。而大吕夹钟以为徵羽。(蕤宾宫之法。)其馀诸律。莫不皆然。不知此法。出于何经。何王所作。何圣所言。投之五声而五声亡。播之六律而六律亡。乐家之大蔀巨祲。未有甚于还宫之法。而一幂千古。蒙不知脱。不亦惑之甚乎。由清为浊。于理未允。于心不安。于是乎半声之说作矣。(见下条。)半声全声。经所不言。因误生误。抑又何益。毁周礼则已。周礼未毁。则此法不可立也。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1L 页
 辨二变声。非三分损益之所生。
辨二变声。非三分损益之所生。《淮南子》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应钟。不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〇孔颖达左传疏曰。(昭二十。)贾逵注周语云。周有七音。谓七律为七器音也。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是五声以外。更加变宫变徵。为七音也。〇镛案淮南子云。角生应钟者。谓姑洗生应钟也。其法黄钟为宫。则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法见上。)若加二变。则须以姑洗下生应钟。又以应钟上生蕤宾。故据之为说。遂以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也。夫以八十一之数。三分损益。其势必五转而穷。(义见前。)故自宫而始。至角而止。又何以三分损益。下生上生乎。牵强锄铻。赘疣枘凿。不可以为法也。
《律吕新书》蔡云。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徵变宫二声。)〇又曰。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则宫不成宫。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然有五音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〇镛案相去一律。相去二律者。试论黄钟一宫。黄钟(宫)、太蔟(商)、姑洗(角)。其相去只隔一律。林钟(徵)、南吕(羽)相去亦然。(未距酉。)惟姑洗(角)、林钟(徵)。隔以二律。(其间隔中吕、蕤宾。)南宫(南吕羽)、黄钟(宫)亦隔二律。(其间隔无射、应钟。)故作变徵变宫。以之承接乎其间也。(十一律皆然。)其说有必不可通者。何也。或隔一律。或隔二律。既云不均。则或隔一律。或相连接。独非不均乎。变徵者。蕤宾也。变宫者。应钟也。(据黄钟之宫而言。)蕤宾与林钟。(徵)相连。(午未律)应钟与黄钟(宫)相连。(亥子律)夫四之与三。名曰不均。而三之与二。号曰太平。非公言也。以法则矫枉而过直。以数则朝三而暮四。圣人之法。顾当若是乎。旦(一作且)蔡氏十二律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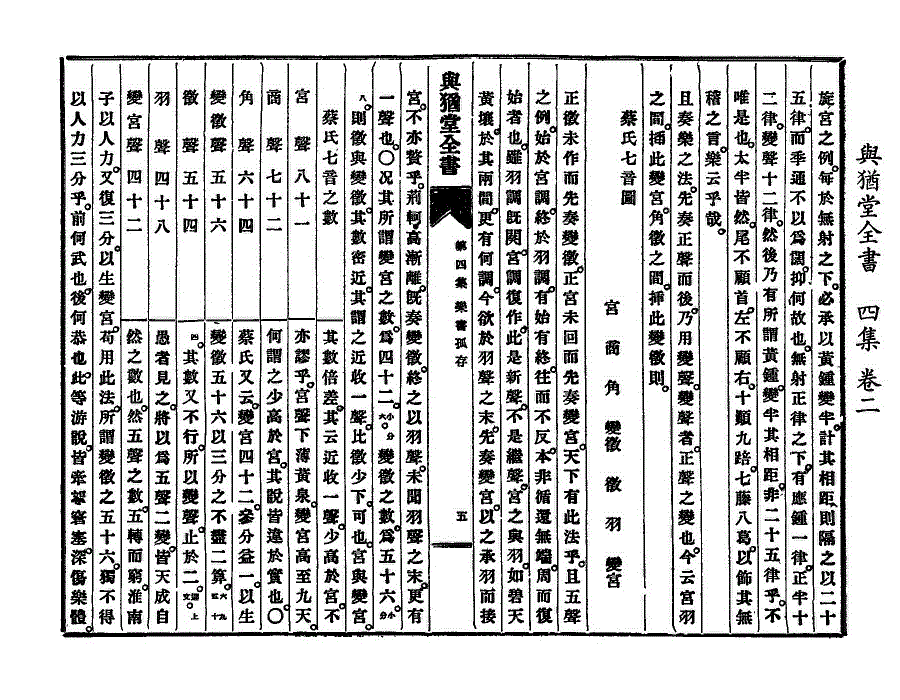 旋宫之例。每于无射之下。必承以黄钟变半。计其相距则隔之以二十五律。而季通不以为阔。抑何故也。无射正律之下。有应钟一律。正半十二律。变声十二律。然后乃有所谓黄钟。变半其相距。非二十五律乎。不唯是也。太半皆然。尾不顾首。左不顾右。十颠九踣。七藤八葛。以饰其无稽之言。乐云乎哉。
旋宫之例。每于无射之下。必承以黄钟变半。计其相距则隔之以二十五律。而季通不以为阔。抑何故也。无射正律之下。有应钟一律。正半十二律。变声十二律。然后乃有所谓黄钟。变半其相距。非二十五律乎。不唯是也。太半皆然。尾不顾首。左不顾右。十颠九踣。七藤八葛。以饰其无稽之言。乐云乎哉。且奏乐之法。先奏正声而后。乃用变声。变声者。正声之变也。今云宫羽之间。插此变宫。角徵之间。插此变徵则。
삽화 새창열기
正徵未作而先奏变徵。正宫未回而先奏变宫。天下有此法乎。且五声之例。始于宫调。终于羽调。有始有终。往而不反。本非循还无端。周而复始者也。虽羽调既阕。宫调复作。此是新声。不是继声。宫之与羽。如碧天黄壤。于其两间。更有何调。今欲于羽声之末。先奏变宫。以之承羽而接宫。不亦赘乎。荆轲、高渐离。既奏变徵。终之以羽声。未闻羽声之末。更有一声也。〇况其所谓变宫之数。为四十二。(小分六。)变徵之数。为五十六。(小分八。)则徵与变徵。其数密近。其谓之近收一声。比徵少下。可也。宫与变宫。
蔡氏七音之数
宫声八十一
商声七十二
角声六十四
变徵声五十六
徵声五十四
羽声四十八
变宫声四十二
其数倍差。其云近收一声。少高于宫。不亦谬乎。宫声下薄黄泉。变宫高至九天。何谓之少高于宫。其说皆违于实也。〇蔡氏又云。变宫四十二。参分益一。以生变徵五十六以(一作二)三分之不尽二算。(六九五十四。)其数又不行。所以变声。止于二。(连上文。)愚者见之。将以为五声二变。皆天成自然之数也。然五声之数。五转而穷。淮南子以人力。又复三分。以生变宫。苟用此法。所谓变徵之五十六。独不得以人力三分乎。前何武也。后何恭也。此等游说。皆牵挐窘塞。深伤乐体。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2L 页
 不可以不辨也。〇总之五声。本无形质。其差清差浊。不可甚分。钟鑮大击。则为宫声。小击则为商声。于其大小之间。击其半声。则名之曰变宫也。变徵之居徵羽之间。其例亦然。若论其度数。则制变宫者。必于宫商之间。执其半数。制变徵者。必于徵羽之间。执其半数。不应偏畸不均。如淮南之法也。所谓变宫黜之在外。姑舍之。试论变徵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而居间之变徵声。乃为五十六。其当于理乎。五十四丝以为徵弦。有一男子。增二丝而为之弦曰。此变徵弦。未有不呵呵拍掌而笑者矣而可乎。〇虽然。隋文帝时。郑译勘校龟玆七调。亦先言宫。次商次角次变徵次徵次羽次变宫。(见通典。)则二变先后之差。非蔡元定之所误。其沿袭已久矣。详见下篇。
不可以不辨也。〇总之五声。本无形质。其差清差浊。不可甚分。钟鑮大击。则为宫声。小击则为商声。于其大小之间。击其半声。则名之曰变宫也。变徵之居徵羽之间。其例亦然。若论其度数。则制变宫者。必于宫商之间。执其半数。制变徵者。必于徵羽之间。执其半数。不应偏畸不均。如淮南之法也。所谓变宫黜之在外。姑舍之。试论变徵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而居间之变徵声。乃为五十六。其当于理乎。五十四丝以为徵弦。有一男子。增二丝而为之弦曰。此变徵弦。未有不呵呵拍掌而笑者矣而可乎。〇虽然。隋文帝时。郑译勘校龟玆七调。亦先言宫。次商次角次变徵次徵次羽次变宫。(见通典。)则二变先后之差。非蔡元定之所误。其沿袭已久矣。详见下篇。辨京房六十律之谬。
《后汉书律历志》汉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数。上使大子大传韦玄成等。亲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〇镛案京房之法。本以十二正律。各生四变律。总之为六十。及其上下相生之后。律管长短。不能循序。故一律所摄。或五或三。参差不同。然其本领则一正。各摄四变。玆设从横表如左。
正律变律第二变第三变第四变
(子)黄钟(下生林)执始(下生去)丙盛(下生安)分勋(下生归)质未(下生否未)林钟(上生蔟)去灭(上生时)安度(上生屈)归嘉(上生随)否与(上生形寅)太蔟(下生南)时息(下生结)屈齐(下生归)随时(下生未)形晋(下生夷酉)南吕(上生姑)结躬(上生变)归期(上生路)未卯(上生形)夷汗(上生依辰)姑洗(下生应)变虞(下生迟)路时(下生未)形始(下生迟)依行(上生包亥)应钟(上生蕤)迟内(上生盛)未育(上生离)迟时(上生制)包育(下生谦午)蕤宾(上生大吕)盛变(上生分)离宫(上生凌)制时(上生少)谦待(上生未)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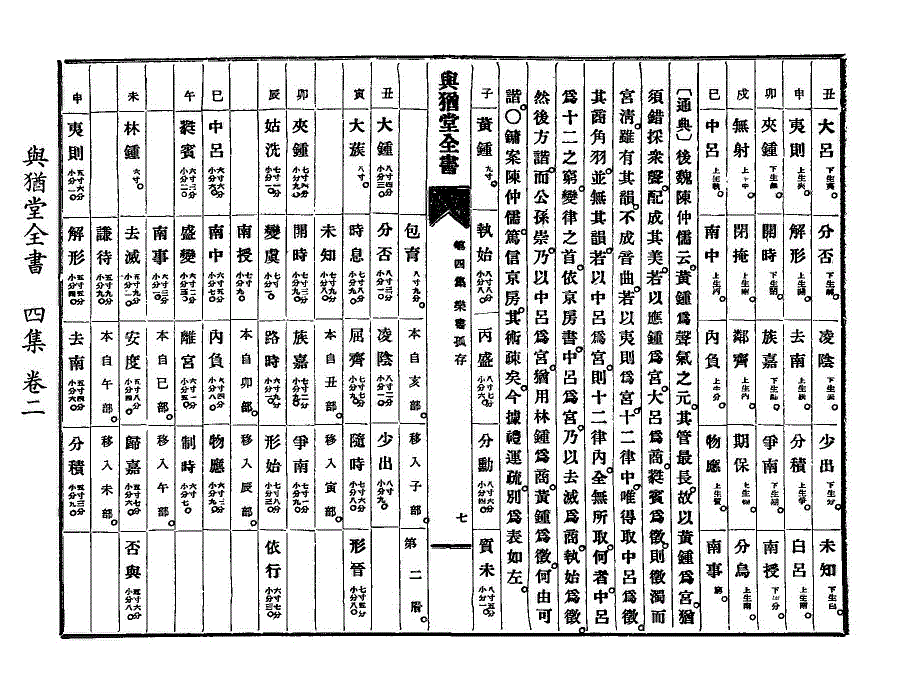 (丑)大吕(下生夷)分否(下生解)凌阴(下生去)少出(下生分)未知(下生白申)夷则(上生夹)解形(上生开)去南(上生族)分积(上生争)白吕(上生南卯)夹钟(下生无)开时(下生闭)族嘉(下生邻)争南(下生期)南授(下生分戌)无射(上生中)闭掩(上生南)邻齐(上生内)期保(上生物)分乌(上生南巳)中吕(上生执)南中(上生丙)内负(上生分)物应(上生质)南事(穷)
(丑)大吕(下生夷)分否(下生解)凌阴(下生去)少出(下生分)未知(下生白申)夷则(上生夹)解形(上生开)去南(上生族)分积(上生争)白吕(上生南卯)夹钟(下生无)开时(下生闭)族嘉(下生邻)争南(下生期)南授(下生分戌)无射(上生中)闭掩(上生南)邻齐(上生内)期保(上生物)分乌(上生南巳)中吕(上生执)南中(上生丙)内负(上生分)物应(上生质)南事(穷)《通典》后魏陈仲儒云。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谐。而公孙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〇镛案陈仲儒。笃信京房。其术疏矣。今据礼运疏。别为表如左。
(子)黄钟(九寸)执始(八寸八分小分八)丙盛(八寸七分小分六)分勋(八寸六分小分四)质未(八寸五分小分一)
包育(八寸九分本自亥部。移入子部。第二层。丑)大钟(八寸四分小分三)分否(八寸三分小分一)凌阴(八寸二分小分一)少出(八寸小分九寅)太蔟(八寸)时息(七寸八分小分九)屈齐(七寸七分小分九)随时(七寸六分小分八)形晋(七寸五分小分八)
未知(七寸九分小分八本自丑部。移入寅部。卯)夹钟(七寸四分小分九)开时(七寸三分小分九)族嘉(七寸二分小分九)争南(七寸一分小分九辰)姑洗(七寸一分小分一)变虞(七寸小分一)路时(六寸九分小分一)形始(七寸八分小分三)依行(六寸七分小分三)
南授(七寸小分九本自卯部。移入辰部。巳)中吕(六寸六分小分六)南中(六寸五分小分七)内负(六寸四分小分八)物应(六寸三分小分九午)蕤宾(六寸三分小分二)盛变(六寸二分小分三)离宫(六寸一分小分五)制时(六寸小分七)
南事(六寸三分小分一本自巳部。移入午部。未)林钟(六寸)去灭(五寸九分小分二)安度(五寸八分小分四)归嘉(五寸七分小分六)否与(五寸六分小分八)
谦待(五寸九分小分九本自午部。移入未部。申)夷则(五寸六分小分二)解形(五寸五分小分四)去南(五寸四分小分六)分积(五寸三分小分九)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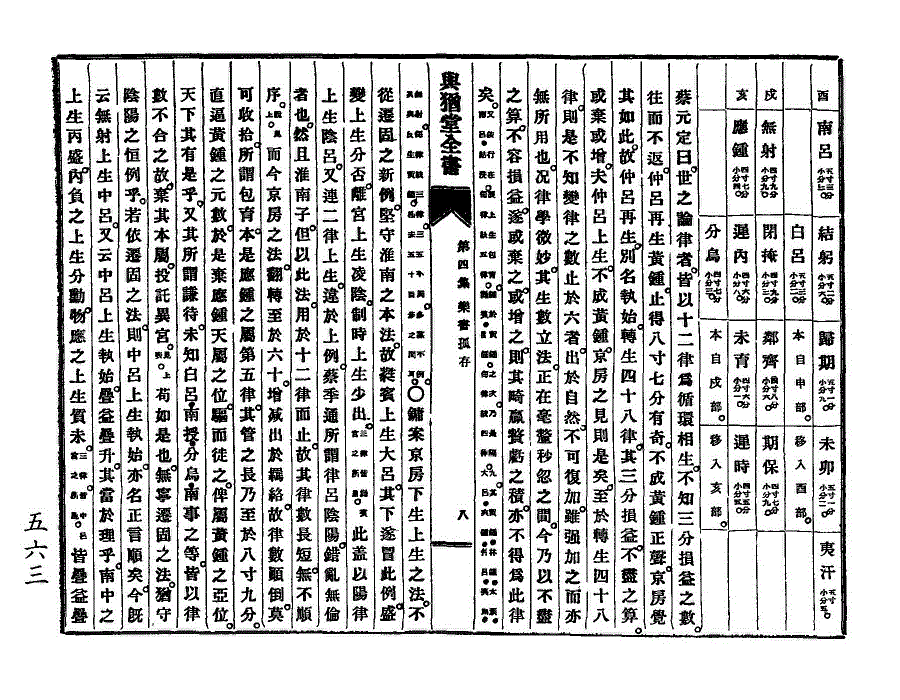 (酉)南吕(五寸三分小分三)结躬(五寸二分小分六)归期(五寸一分小分九)未卯(五寸一分小分二)夷汗(五寸小分五)
(酉)南吕(五寸三分小分三)结躬(五寸二分小分六)归期(五寸一分小分九)未卯(五寸一分小分二)夷汗(五寸小分五)白吕(五寸三分小分二本自申部。移入酉部。戌)无射(四寸九分小分九)闭掩(四寸九分小分三)邻齐(四寸八分小分六)期保(四寸七分小分九亥)应钟(四寸七分小分四)迟内(四寸六分小分八)未育(四寸六分小分一)迟时(四寸五分小分五)
分乌(四寸七分小分三本自戌部。移入亥部。)
蔡元定曰。世之论律者。皆以十二律为循环相生。不知三分损益之数。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钟。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钟正声。京房觉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执始。转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损益。不尽之算。或弃或增。夫仲吕上生。不成黄钟。京房之见则是矣。至于转生四十八律。则是不知变律之数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复加。虽强加之而亦无所用也。况律学微妙。其生数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间。今乃以不尽之算。不容损益。遂或弃之。或增之。则其畸赢赘亏之积。亦不得为此律矣。(又依行在辰上生包育。编于黄钟之次。乃是隔九。其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每律统五律。蕤宾、应钟。每律统四律。大吕、夹钟、仲吕、夷则、无射。每律统三律。三五不周。多寡不例。其与反生黄钟。相去五十百步之间耳。)〇镛案京房下生上生之法。不从迁固之新例。坚守淮南之本法。故蕤宾上生大吕。其下遂冒此例。盛变上生分否。离宫上生凌阴。制时上生少出。(三律皆蕤宾宫之所属。)此盖以阳律上生阴吕。又连二律上生。违于上例。蔡季通所谓律吕阴阳。错乱无伦者也。然且淮南子。但以此法。用于十二律而止。故其律数长短。无不顺序。(说见上。)而今京房之法。翻转至于六十。增减出于羁络。故律数颠倒。莫可收拾。所谓包育。本是应钟之属第五律。其管之长乃至于八寸九分。直逼黄钟之元数。于是弃应钟天属之位。驱而徙之。俾属黄钟之亚位。天下其有是乎。又其所谓谦待。未知白吕、南授、分乌、南事之等。皆以律数不合之故。弃其本属。投托异宫。(见上表。)苟如是也。无宁迁固之法。犹守阴阳之恒例乎。若依迁固之法。则中吕上生执始。亦名正言顺矣。今既云无射上生中吕。又云中吕上生执始。叠益叠升。其当于理乎。南中之上生丙盛。内负之上生分勋。物应之上生质未。(三律。皆中吕宫之所属。)皆叠益叠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4H 页
 升。又所谓依行之上。生包育。自乱其例。无复规画。(淮南子叠升之法。自蕤宾始也。今依行。本以姑洗宫之属。已令叠升。是自乱其例。)作法如此。犹欲建诸当世。传诸后世。不亦难乎。〇总之。六十律之说。必自古有之。非房之所创言也。十二律。文之以五声。(周礼文)非六十乎。然律尺长短。本据钟声。钟既十二。律亦十二。每于一律。各具五声。计其声则六十也。而立其律。则十二而已。于此十二之中。任取其一。立之为宫。顺取其四。以备四声。(即周礼二至奏乐之法。)合乐之法。如斯而已。平易和顺。通豁无滞。未有甚于律吕之法。唯是邹吕之学。七藤八葛。左绾右纠。而乐于是亡矣。子母相生之说生。则林钟。据大吕之位。而六律之配匹。悉乱。十二还宫之说作。则执始。篡黄钟之位。而六律之度数无限。乐道之亡。不由是二者乎。蔡元定谓变律止六。而深斥京房之法。然五声有变声。六律无变律。既变至六。则十二可也。四十八亦可也。何得以五十步。笑百步哉。〇又按京房之法。以律配日。以占六气。又云得位者生五子。(谓黄钟、大蔟、姑洗、林钟、南吕之宫。各摄五律。)失位者生三子。(谓大吕、夹钟、中吕、夷则、无射之等。各摄三律。)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谓蕤宾应钟之宫。各摄四律。)此等邪说。皆支离蔓结。不能尽锄。令姑略之。(京房之法。名虽六十。而分寸多同。大蔟少出。均为八寸。变虞。南授等是七寸。唯以其小分零畸。为之第次。以之制琴而丝数不明。以之铸钟而径围难定。虽留无用。必焚乃可者也。)
升。又所谓依行之上。生包育。自乱其例。无复规画。(淮南子叠升之法。自蕤宾始也。今依行。本以姑洗宫之属。已令叠升。是自乱其例。)作法如此。犹欲建诸当世。传诸后世。不亦难乎。〇总之。六十律之说。必自古有之。非房之所创言也。十二律。文之以五声。(周礼文)非六十乎。然律尺长短。本据钟声。钟既十二。律亦十二。每于一律。各具五声。计其声则六十也。而立其律。则十二而已。于此十二之中。任取其一。立之为宫。顺取其四。以备四声。(即周礼二至奏乐之法。)合乐之法。如斯而已。平易和顺。通豁无滞。未有甚于律吕之法。唯是邹吕之学。七藤八葛。左绾右纠。而乐于是亡矣。子母相生之说生。则林钟。据大吕之位。而六律之配匹。悉乱。十二还宫之说作。则执始。篡黄钟之位。而六律之度数无限。乐道之亡。不由是二者乎。蔡元定谓变律止六。而深斥京房之法。然五声有变声。六律无变律。既变至六。则十二可也。四十八亦可也。何得以五十步。笑百步哉。〇又按京房之法。以律配日。以占六气。又云得位者生五子。(谓黄钟、大蔟、姑洗、林钟、南吕之宫。各摄五律。)失位者生三子。(谓大吕、夹钟、中吕、夷则、无射之等。各摄三律。)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谓蕤宾应钟之宫。各摄四律。)此等邪说。皆支离蔓结。不能尽锄。令姑略之。(京房之法。名虽六十。而分寸多同。大蔟少出。均为八寸。变虞。南授等是七寸。唯以其小分零畸。为之第次。以之制琴而丝数不明。以之铸钟而径围难定。虽留无用。必焚乃可者也。)辨钱乐之三百律。万宝常千八声。皆出旋官(一作宫)之法。
《通考》宋元嘉中太史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馀。更生三百律。〇梁博士沈重钟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乃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自黄钟。终于壮进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损一以下生。自依行终于亿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运一律。为终其数。皆取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以九三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馀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长也。(黄钟一部三十四律。大吕一部二十七律。大蔟一部三十四律。林钟一部三十四律。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南吕一部三十四律。无射一部二十七律。应钟一部二十八律。)〇镛案律历。本不相关。特以历家有差法。其不尽之数。须以九数析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4L 页
 之。或有究竟。以此之故。西京之法。律历二家。或相资籍。岂知好事如钱沈者。竟作三百六十律。以应一期之日哉。斯皆乐家之灾孽。锄(一作锄)之不清。即古乐无还魂之日也。
之。或有究竟。以此之故。西京之法。律历二家。或相资籍。岂知好事如钱沈者。竟作三百六十律。以应一期之日哉。斯皆乐家之灾孽。锄(一作锄)之不清。即古乐无还魂之日也。《通典》隋文帝时。有万宝常者。妙通钟律。偏解六音。常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文帝后召见。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对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遂从之。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于译调二律。并撰六乐谱十四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丝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千八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时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〇镛案水尺者。如京房律准之类也。其法先作铜尺。刻画分寸。另于玻瓈管内。盛水缄口。安置尺上。以察平仄。盖此玻瓈水管之内。例有一点气球。白如银汞。尺面少仄。气球必走向高处去。以此水平。可验地平。此所谓水尺也。不知万氏所用。亦果此物乎。律准本欲极平。其上另设弦柱。使其移柱之时。弦无高下也。弦高则声急。弦下则声缓。所以谨也。然万宝常改丝移柱之变。都不出还宫八十四调谬戾之法。则其所撰六乐谱十四卷。亦幸哉其无传也。一千八声。谁能辨之。妄甚矣。
辨十二律。无半声变半声之用。
《汉书律历志》黄钟为宫。则大蔟姑洗林钟南吕。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谓无残分也。)不复与他律为役者。同心一统之义也。他律虽当其月自宫者。其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钟至尊。无与并也。〇杜佑云。凫氏为钟。以律计身倍半。(贾疏云。假令黄钟之律。长九寸。以律计身倍半为钟。倍九寸为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为钟。馀律亦如是。)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律。制为十二子声。但先儒释用倍声。自有二义。一义云半以十二正律。为十二子声之钟。先(一作此)即正半声。 一义云。于中吕之管。三分益一。上生黄钟。(即变律。)然后半之。以为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5H 页
 子声之钟。(此即变半声。)其为半正声之法者。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为均。子声则四寸半。(林钟以下。皆照此例。以为子声。)其为半相生之法者。以中吕之管六寸。上生黄钟。(得八寸零。)黄钟下生林钟。三分去一。还以所得林钟之管寸数半之。以为林钟子声之管。(大蔟以下。皆照此例。以为子声。)上下相生。终于中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半之。各以为子声之律。故有二十四钟。〇蔡元定云。十二律有十二子声。所谓正半律也。又自中吕。上生黄钟八寸零。(本云。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声。即所谓变律。变半律也。〇镛案汉书。虽无半声之说。乃有正声之称。有正声则应有不正之声。此班固阴用京房之律法。欲使五声大小之数。顺而无逆也。半声变半声之说。虽称先儒有释。其著之为法。自杜氏始也。律吕新书。以之为八十四声。今依通考。列其分寸。以便考校。
子声之钟。(此即变半声。)其为半正声之法者。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为均。子声则四寸半。(林钟以下。皆照此例。以为子声。)其为半相生之法者。以中吕之管六寸。上生黄钟。(得八寸零。)黄钟下生林钟。三分去一。还以所得林钟之管寸数半之。以为林钟子声之管。(大蔟以下。皆照此例。以为子声。)上下相生。终于中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半之。各以为子声之律。故有二十四钟。〇蔡元定云。十二律有十二子声。所谓正半律也。又自中吕。上生黄钟八寸零。(本云。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声。即所谓变律。变半律也。〇镛案汉书。虽无半声之说。乃有正声之称。有正声则应有不正之声。此班固阴用京房之律法。欲使五声大小之数。顺而无逆也。半声变半声之说。虽称先儒有释。其著之为法。自杜氏始也。律吕新书。以之为八十四声。今依通考。列其分寸。以便考校。正变全半分寸表正律正半声变律变半声
(子)黄钟(九寸无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丝二忽不用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丝一忽丑)大吕(八寸三分七釐一毫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寅)太蔟(八寸四寸七寸八分二毫四丝四忽七初不用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丝六忽八初卯)夹钟(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丝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丝辰)姑洗(七寸一分三寸五分七寸一釐二毫二丝二初二抄不用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二丝一初一抄巳)中吕(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丝六忽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丝三忽午)蕤宾(六寸二分八釐三寸一分四釐)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5L 页
 (未)林钟(六寸三寸不用)五寸八分五釐四毫一绿(一作丝)一忽三初(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丝六初申)夷则(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二寸七分二釐五毫酉)南吕(五寸三分二寸六分不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丝一初一抄二寸五分六釐七丝四忽五初七抄戌)无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丝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丝亥)应钟(四寸六分六釐二寸三分三釐不用四寸六分七毫四丝三忽一初四丝三分抄之一二寸三分三毫六丝六忽六抄三分抄之一不用)
(未)林钟(六寸三寸不用)五寸八分五釐四毫一绿(一作丝)一忽三初(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丝六初申)夷则(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二寸七分二釐五毫酉)南吕(五寸三分二寸六分不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丝一初一抄二寸五分六釐七丝四忽五初七抄戌)无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丝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丝亥)应钟(四寸六分六釐二寸三分三釐不用四寸六分七毫四丝三忽一初四丝三分抄之一二寸三分三毫六丝六忽六抄三分抄之一不用)삽화 새창열기
蔡云。按通典。正变及半。凡四十八声。上下相生。最得汉志所谓黄钟不复为他律役之意。与律书五声大小次第之法。但变律。止于应钟。虽设而无所用。则其实三十六声而已。其间阳律不用变声。而黄钟又不用正半声。阴吕不用正半声。而应钟又不用变半声。其实又二十八声而已。〇镛案所谓变律。杜氏蔡氏虽讳其名。此是京房所作执始(黄钟变。)时息(大蔟变。)变虞(姑洗变。)去灭(林钟变。)结躬(南吕变。)迟内(应钟变。)之等改头换面者。非他物也。特京房全用十二。蔡氏选用其六耳。今未论他事。林钟之变半声二寸八分零。南吕之变半声二寸五分零。应钟之变半声二寸三分零。照此制管。使乐工吹之。以之节八音而行八风。天下有此事乎。奚但变半然矣。即其所谓正半声。亦未尝不然也。今取正半变半各二声。准古尺为管。图列如上。
试观此物。有能吹之作声者乎。吹之作声。能正五音。均八器。为韶为武。以之荐郊庙而礼宾客乎。其物为妖物。其言为伪言。犹复奉之为经意。或天地造化之理。寓乎其中。不亦妄乎。通典曰。无射子声之律。二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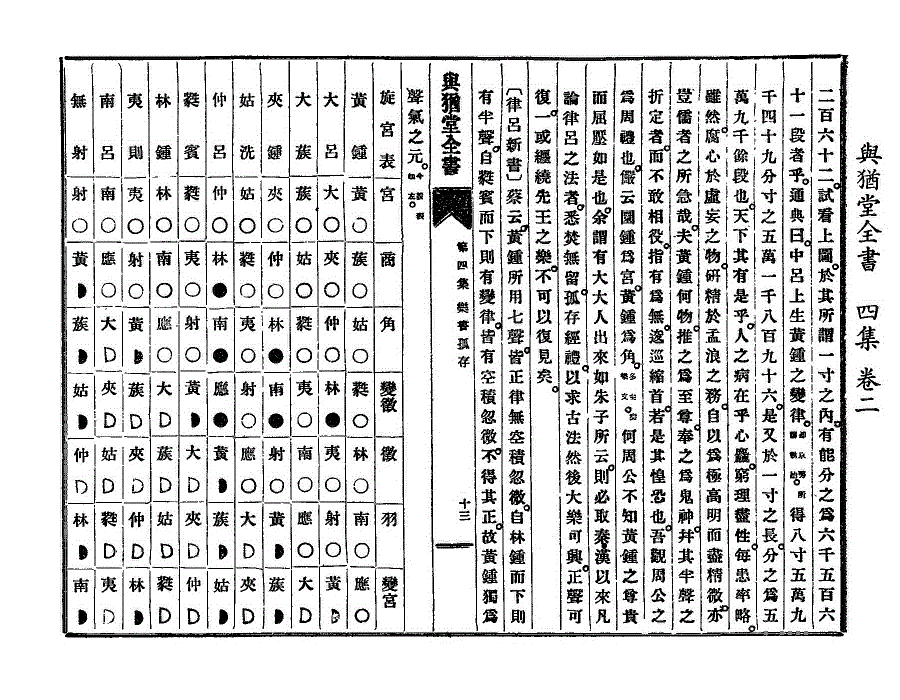 二百六十二。试看上图。于其所谓一寸之内。有能分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段者乎。通典曰。中吕上生黄钟之变律。(即京房所谓执始。)得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是又于一寸之长。分之为五万九千馀段也。天下其有是乎。人之病在乎心粗。穷理尽性。每患率略。虽然。腐心于虚妄之物。研精于孟浪之务。自以为极高明而尽精微。亦岂儒者之所急哉。夫黄钟何物。推之为至尊。奉之为鬼神。并其半声之折定者。而不敢相役。指有为无。逡巡缩首。若是其惶恐也。吾观周公之为周礼也。俨云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冬至奏乐文。)何周公不知黄钟之尊贵而屈压如是也。余谓有大大人出来如朱子所云。则必取秦、汉以来凡论律吕之法者。悉焚无留。孤存经礼。以求古法然后大乐可兴。正声可复。一或缠绕先王之乐。不可以复见矣。
二百六十二。试看上图。于其所谓一寸之内。有能分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段者乎。通典曰。中吕上生黄钟之变律。(即京房所谓执始。)得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是又于一寸之长。分之为五万九千馀段也。天下其有是乎。人之病在乎心粗。穷理尽性。每患率略。虽然。腐心于虚妄之物。研精于孟浪之务。自以为极高明而尽精微。亦岂儒者之所急哉。夫黄钟何物。推之为至尊。奉之为鬼神。并其半声之折定者。而不敢相役。指有为无。逡巡缩首。若是其惶恐也。吾观周公之为周礼也。俨云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冬至奏乐文。)何周公不知黄钟之尊贵而屈压如是也。余谓有大大人出来如朱子所云。则必取秦、汉以来凡论律吕之法者。悉焚无留。孤存经礼。以求古法然后大乐可兴。正声可复。一或缠绕先王之乐。不可以复见矣。《律吕新书》蔡云。黄钟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今设表如左。)
旋宫表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
黄钟黄 ○蔟 ○姑 ○蕤 ○林 ○南 ○应 ○
大吕大 ○夹 ○仲 ○林 ●夷 ○射 ○黄 ▶
太蔟蔟 ○姑 ○蕤 ○夷 ○南 ○应 ○大 ▷
夹钟夹 ○仲 ○林 ●南 ●射 ○黄 ▶蔟 ▶
姑洗姑 ○蕤 ○夷 ○射 ○应 ○大 ▷夹 ▷
仲吕仲 ○林 ●南 ●应 ●黄 ▶蔟 ▶姑 ▶
蕤宾蕤 ○夷 ○射 ○黄 ▶大 ▷夹 ▷仲 ▷
林钟林 ○南 ○应 ○大 ▷蔟 ▷姑 ▷蕤 ▷
夷则夷 ○射 ○黄 ▶蔟 ▷夹 ▷仲 ▷林 ▶
南吕南 ○应 ○大 ▷夹 ▷姑 ▷蕤 ▷夷 ▷
无射射 ○黄 ▶蔟 ▶姑 ▶仲 ▷林 ▶南 ▶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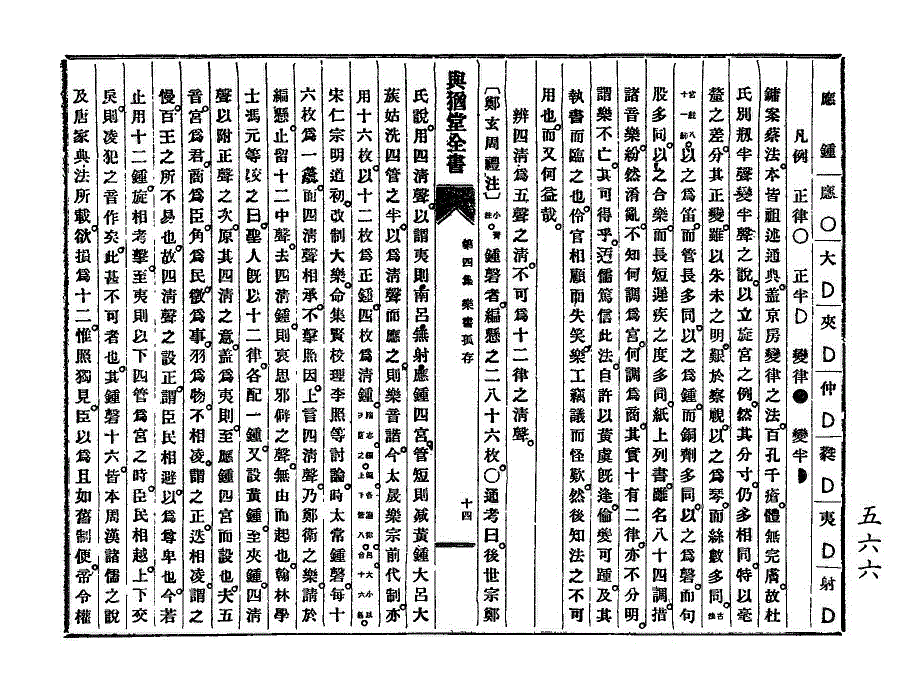 应钟应 ○大 ▷夹 ▷仲 ▷蕤 ▷夷 ▷射 ▷
应钟应 ○大 ▷夹 ▷仲 ▷蕤 ▷夷 ▷射 ▷凡例 正律○ 正半▷ 变律● 变半▶
镛案蔡法。本皆祖述通典。盖京房变律之法。百孔千疮。体无完肤。故杜氏别创半声变半声之说。以立旋宫之例。然其分寸。仍多相同。特以毫釐之差。分其正变。虽以朱未(离朱)之明。艰于察视。以之为琴。而丝数多同。(古法宫弦八十一丝。)以之为笛。而管长多同。以之为钟。而铜剂多同。以之为磬。而句股多同。以之合乐。而长短迟疾之度多同。纸上列书。虽名八十四调。措诸音乐。纷然淆乱。不知何调为宫。何调为商。其实十有二律。亦不分明。谓乐不亡。其可得乎。迂儒笃信此法。自许以黄虞既逢。伦夔可踵。及其执书而临之也。伶官相顾而失笑。乐工窃议而怪叹。然后知法之不可用也。而又何益哉。
辨四清为五声之清。不可为十二律之清声。
《郑玄周礼注》(小胥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〇通考曰。后世宗郑氏说。用四清声。以谓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四宫。管短则减黄钟大吕大蔟姑洗四管之半。以为清声而应之。则乐音谐。今太晟乐宗前代制。亦用十六枚。以十二枚为正钟。四枚为清钟。(隋志。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讨论。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悬。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翰林学士冯元等駮之曰。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所不易也。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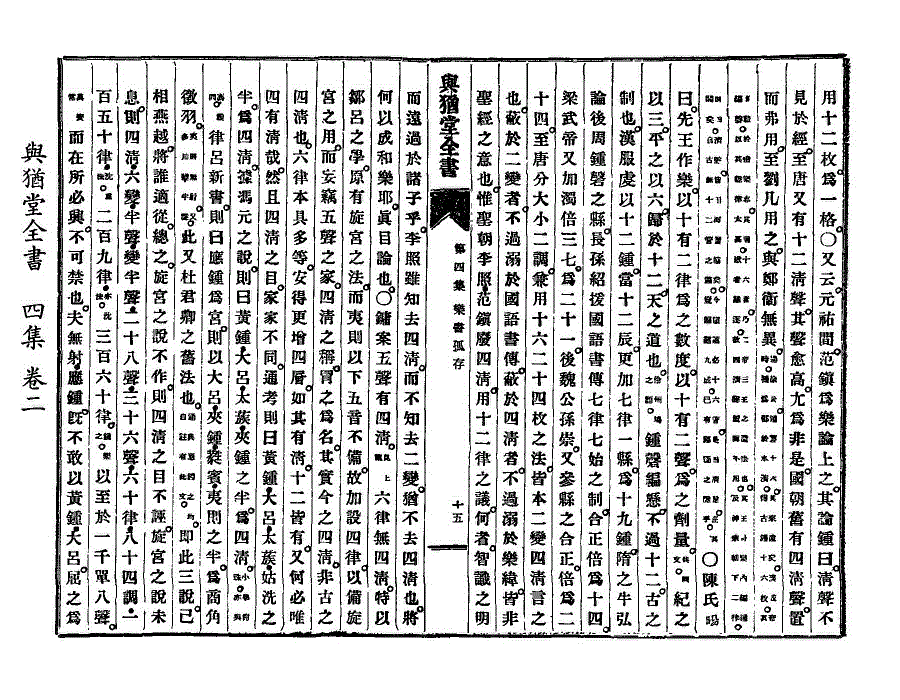 用十二枚。为一格。〇又云。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清声不见于经。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徐云。钟磬十六。其来远矣。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钟十六枚。其事载于礼乐志。其称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今镇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已有郑卫之声乎。)〇陈氏(旸)曰。先王作乐。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剂量。(典同文。)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归于十二。天之道也。(伶州鸠之语。)钟磬编悬。不过十二。古之制也。汉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之牛弘论后周钟磬之县。长孙绍援国语书传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为十四。梁武帝又加浊倍三七。为二十一。后魏公孙崇。又参县之合正。倍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调。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变四清言之也。蔽于二变者。不过溺于国语书传。蔽于四清者。不过溺于乐纬。皆非圣经之意也。惟圣朝李照、范镇废四清。用十二律之议。何者。智识之明而远过于诸子乎。李照虽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变。犹不去四清也。将何以成和乐耶。真目论也。〇镛案五声有四清。(见上篇)六律无四清。特以邹吕之学。原有旋宫之法。而夷则以下五音不备。故加设四律。以备旋宫之用。而妄窃五声之家。四清之称。冒之为名。其实今之四清。非古之四清也。六律本具多等。安得更增四层。如其有清。十二皆有。又何必唯四有清哉。然且四清之目。家家不同。通考则曰黄钟、大吕、太蔟、姑洗之半。为四清。据冯元之说。则曰黄钟、大吕、太蔟、夹钟之半。为四清。(小学绀珠。亦与冯说同。)律吕新书。则曰应钟为宫。则以大吕、夹钟、蕤宾、夷则之半。为商角徵羽。(夷则无射。又多用变半声。)此又杜君卿之旧法也。(通典应钟之均。自注有此文。)即此三说。已相燕越。将谁适从。总之。旋宫之说不作。则四清之目不诬。旋宫之说未息。则四清、六变、半声、变半声、二十八声、三十六声、六十律、八十四调、一百五十律(沈重法)、二百九律(亦沈法)、三百六十律(钱乐之)。以至于一千单八声。(万宝常)而在所必兴。不可禁也。夫无射、应钟。既不敢以黄钟、大吕。屈之为
用十二枚。为一格。〇又云。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清声不见于经。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徐云。钟磬十六。其来远矣。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钟十六枚。其事载于礼乐志。其称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今镇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已有郑卫之声乎。)〇陈氏(旸)曰。先王作乐。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剂量。(典同文。)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归于十二。天之道也。(伶州鸠之语。)钟磬编悬。不过十二。古之制也。汉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之牛弘论后周钟磬之县。长孙绍援国语书传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为十四。梁武帝又加浊倍三七。为二十一。后魏公孙崇。又参县之合正。倍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调。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变四清言之也。蔽于二变者。不过溺于国语书传。蔽于四清者。不过溺于乐纬。皆非圣经之意也。惟圣朝李照、范镇废四清。用十二律之议。何者。智识之明而远过于诸子乎。李照虽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变。犹不去四清也。将何以成和乐耶。真目论也。〇镛案五声有四清。(见上篇)六律无四清。特以邹吕之学。原有旋宫之法。而夷则以下五音不备。故加设四律。以备旋宫之用。而妄窃五声之家。四清之称。冒之为名。其实今之四清。非古之四清也。六律本具多等。安得更增四层。如其有清。十二皆有。又何必唯四有清哉。然且四清之目。家家不同。通考则曰黄钟、大吕、太蔟、姑洗之半。为四清。据冯元之说。则曰黄钟、大吕、太蔟、夹钟之半。为四清。(小学绀珠。亦与冯说同。)律吕新书。则曰应钟为宫。则以大吕、夹钟、蕤宾、夷则之半。为商角徵羽。(夷则无射。又多用变半声。)此又杜君卿之旧法也。(通典应钟之均。自注有此文。)即此三说。已相燕越。将谁适从。总之。旋宫之说不作。则四清之目不诬。旋宫之说未息。则四清、六变、半声、变半声、二十八声、三十六声、六十律、八十四调、一百五十律(沈重法)、二百九律(亦沈法)、三百六十律(钱乐之)。以至于一千单八声。(万宝常)而在所必兴。不可禁也。夫无射、应钟。既不敢以黄钟、大吕。屈之为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7L 页
 商徵。则旋相为宫之义。破已久矣。又何以纷纭猜摸。曰清曰变曰四曰六。要以粉饰。此旋宫之谬义哉。惑之甚矣。〇至于周礼小胥之注。郑以汉法解周礼。不足据也。郑人以歌钟二肆。女乐二八。赂晋侯。(襄十一。)郑玄谓女乐以二八为队。歌钟亦当十六。然郑玄以十六为一堵。杜预以十六为一肆。其无古训。即此可知。汉家乐律。自元帝粗备。而京房还宫之法。为世所宗。至班固作志。正声半声。已见一斑。当时钟磬之十六为剂。可胜言哉。郑习见此物。遂以十六为一簴。其实经无正文。典同职明云。乐器以十有二。为之数度。以十有二。为之剂量。何苦舍此赫奕之经文。而必郑氏之注。是崇是信哉。借如其说。四清之钟。用以还宫。则自天子达于士。十六不可少也。郑乃云。诸侯之卿。用其半。不用其全。用其半则八钟而已。以之为一宫之均。则剩其一。以之为还宫之法。则缺其八。将安用之。四清之目。起于后世。非圣经之所得有也。〇又按陈氏痛斥二变四清。其义正矣。但五声之家。不能无二变四清。(义见前。)四清起于后世。去之犹可。二变。明载国语。不可经击。但不可以十有二律。配之为二变。配之为四清也。
商徵。则旋相为宫之义。破已久矣。又何以纷纭猜摸。曰清曰变曰四曰六。要以粉饰。此旋宫之谬义哉。惑之甚矣。〇至于周礼小胥之注。郑以汉法解周礼。不足据也。郑人以歌钟二肆。女乐二八。赂晋侯。(襄十一。)郑玄谓女乐以二八为队。歌钟亦当十六。然郑玄以十六为一堵。杜预以十六为一肆。其无古训。即此可知。汉家乐律。自元帝粗备。而京房还宫之法。为世所宗。至班固作志。正声半声。已见一斑。当时钟磬之十六为剂。可胜言哉。郑习见此物。遂以十六为一簴。其实经无正文。典同职明云。乐器以十有二。为之数度。以十有二。为之剂量。何苦舍此赫奕之经文。而必郑氏之注。是崇是信哉。借如其说。四清之钟。用以还宫。则自天子达于士。十六不可少也。郑乃云。诸侯之卿。用其半。不用其全。用其半则八钟而已。以之为一宫之均。则剩其一。以之为还宫之法。则缺其八。将安用之。四清之目。起于后世。非圣经之所得有也。〇又按陈氏痛斥二变四清。其义正矣。但五声之家。不能无二变四清。(义见前。)四清起于后世。去之犹可。二变。明载国语。不可经击。但不可以十有二律。配之为二变。配之为四清也。辨京房立准之法。即律家之异端。
《后汉书律历志》汉元帝时。郎中京房曰。竹声不可以调度。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〇范晔云。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辨。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止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〇镛案京房所谓竹声不可以调度者。律管之谓也。既不调度何名为律。伶州鸠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而房之言如此。今律之非古律。不既明甚乎。范蔚宗。欲截管为律。以立道本。刻木为准。按画求声则惑之甚矣。夫可行之谓道。不行非道也。今据京房之说。竹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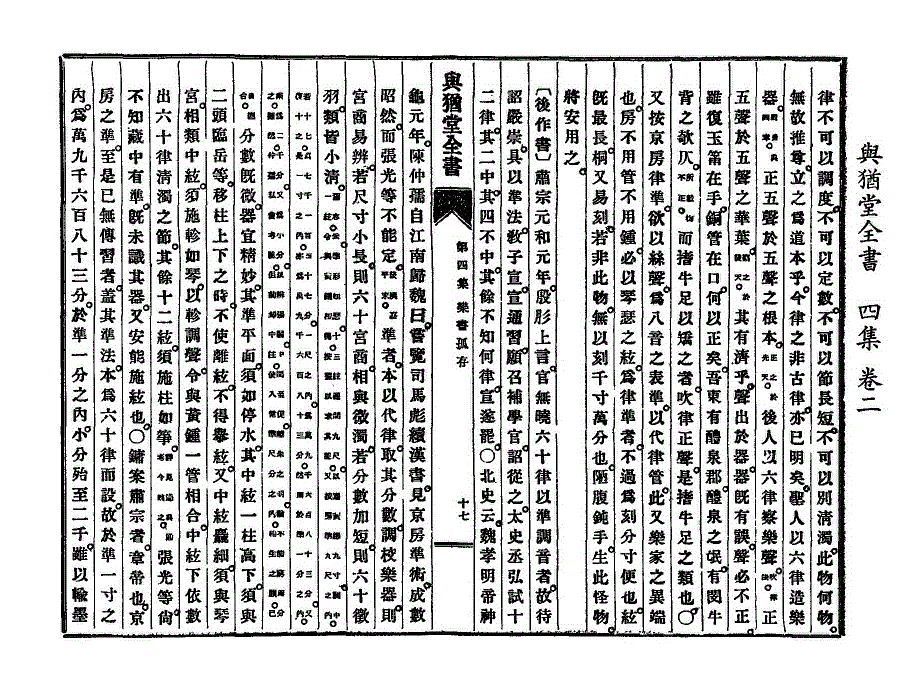 律不可以调度。不可以定数。不可以节长短。不可以别清浊。此物何物。无故推尊。立之为道本乎。今律之非古律。亦已明矣。圣人以六律造乐器。(周礼典同章。)正五声于五声之根本。(正之于先天。)后人以六律察乐声。(吹律法。)正五声于五声之华叶。(察之于后天。)其有济乎。声出于器。器既有误。声必不正。虽复玉筒在手。铜管在口。何以正矣。吾东有醴泉郡。醴泉之氓。有闵牛背之欹仄。(所戴物不正。)而支牛足以矫之者。吹律正声。是支牛足之类也。〇又按京房律准。欲以丝声。为八音之表准。以代律管。此又乐家之异端也。房不用管不用钟。必以琴瑟之弦。为律准者。不过为刻分寸便也。弦既最长。桐又易刻。若非此物。无以刻千寸万分也。陋腹钝手。生此怪物。将安用之。
律不可以调度。不可以定数。不可以节长短。不可以别清浊。此物何物。无故推尊。立之为道本乎。今律之非古律。亦已明矣。圣人以六律造乐器。(周礼典同章。)正五声于五声之根本。(正之于先天。)后人以六律察乐声。(吹律法。)正五声于五声之华叶。(察之于后天。)其有济乎。声出于器。器既有误。声必不正。虽复玉筒在手。铜管在口。何以正矣。吾东有醴泉郡。醴泉之氓。有闵牛背之欹仄。(所戴物不正。)而支牛足以矫之者。吹律正声。是支牛足之类也。〇又按京房律准。欲以丝声。为八音之表准。以代律管。此又乐家之异端也。房不用管不用钟。必以琴瑟之弦。为律准者。不过为刻分寸便也。弦既最长。桐又易刻。若非此物。无以刻千寸万分也。陋腹钝手。生此怪物。将安用之。《后作书(后汉书)》肃宗元和元年。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宣。宣通习。愿召补学官。诏从之。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馀不知何律。宣遂罢。〇北史云。魏孝明帝神龟元年。陈仲孺自江南归魏曰。尝览司马彪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昭然。而张光等不能定。(后汉嘉平末。)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旧志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按画以求其声。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孺私会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馀十二弦。须施柱如筝。(详见通典通考今略之。)张光等。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安能施弦也。〇镛案肃宗者。章帝也。京房之准。至是已无传习者。盖其准法。本为六十律而设。故于准一寸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于准一分之内。小分殆至二千。虽以输墨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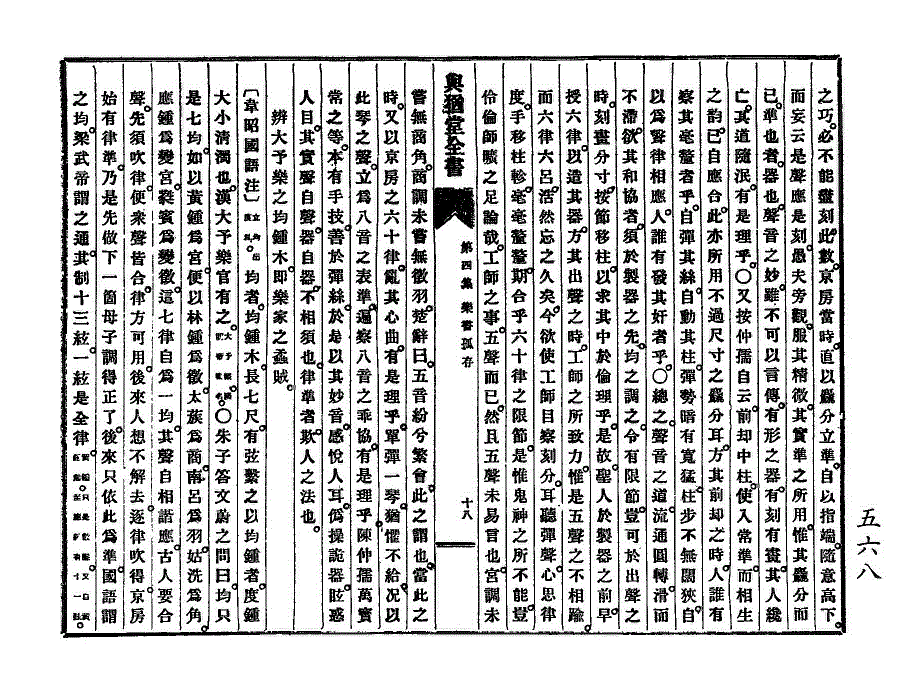 之巧。必不能尽刻。此数。京房当时。直以粗分立准。自以指端。随意高下。而妄云是声应是刻。愚夫旁观。服其精微。其实准之所用。惟其粗分而已。准也者。器也。声音之妙。虽不可以言传。有形之器。有刻有画。其人才亡。其道随泯。有是理乎。〇又按仲孺自云。前却中柱。使入常准。而相生之韵。已自应合。此亦所用不过尺寸之粗分耳。方其前却之时。人谁有察其毫釐者乎。自弹其丝。自动其柱。弹势暗有宽猛。柱步不无阔狭。自以为声律相应。人谁有发其奸者乎。〇总之。声音之道。流通圆转。滑而不滞。欲其和协者。须于制器之先。均之调之。令有限节。岂可于出声之时。刻画分寸。按节移柱。以求其中于伦理乎。是故。圣人于制器之前。早授六律。以造其器。方其出声之时。工师之所致力。惟是五声之不相踰。而六律六吕。浩然忘之久矣。今欲使工师目察刻分。耳听弹声。心思律度。手移柱轸。毫毫釐釐。期合乎六十律之限节。是惟鬼神之所不能。岂伶伦师旷之足论哉。工师之事。五声而已。然且五声未易言也。宫调未尝无商角。商调未尝无徵羽。楚辞曰。五音纷兮繁会。此之谓也。当此之时。又以京房之六十律。乱其心曲。有是理乎。单弹一琴。犹惧不给。况以此琴之声。立为八音之表准。遍察八音之乖协。有是理乎。陈仲孺万宝常之等。本有手技。善于弹丝。于是以其妙音。感悦人耳。伪操诡器。眩惑人目。其实声自声。器自器。不相须也。律准者。欺人之法也。
之巧。必不能尽刻。此数。京房当时。直以粗分立准。自以指端。随意高下。而妄云是声应是刻。愚夫旁观。服其精微。其实准之所用。惟其粗分而已。准也者。器也。声音之妙。虽不可以言传。有形之器。有刻有画。其人才亡。其道随泯。有是理乎。〇又按仲孺自云。前却中柱。使入常准。而相生之韵。已自应合。此亦所用不过尺寸之粗分耳。方其前却之时。人谁有察其毫釐者乎。自弹其丝。自动其柱。弹势暗有宽猛。柱步不无阔狭。自以为声律相应。人谁有发其奸者乎。〇总之。声音之道。流通圆转。滑而不滞。欲其和协者。须于制器之先。均之调之。令有限节。岂可于出声之时。刻画分寸。按节移柱。以求其中于伦理乎。是故。圣人于制器之前。早授六律。以造其器。方其出声之时。工师之所致力。惟是五声之不相踰。而六律六吕。浩然忘之久矣。今欲使工师目察刻分。耳听弹声。心思律度。手移柱轸。毫毫釐釐。期合乎六十律之限节。是惟鬼神之所不能。岂伶伦师旷之足论哉。工师之事。五声而已。然且五声未易言也。宫调未尝无商角。商调未尝无徵羽。楚辞曰。五音纷兮繁会。此之谓也。当此之时。又以京房之六十律。乱其心曲。有是理乎。单弹一琴。犹惧不给。况以此琴之声。立为八音之表准。遍察八音之乖协。有是理乎。陈仲孺万宝常之等。本有手技。善于弹丝。于是以其妙音。感悦人耳。伪操诡器。眩惑人目。其实声自声。器自器。不相须也。律准者。欺人之法也。辨大予乐之均钟木。即乐家之蟊贼。
《韦昭国语注》(立均出度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官有之。(大予乐。汉明帝乐名。)〇朱子答文蔚之问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钟为宫。便以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为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黄钟只是散声。又自黄钟起。至应钟有十一弦(一作弦)。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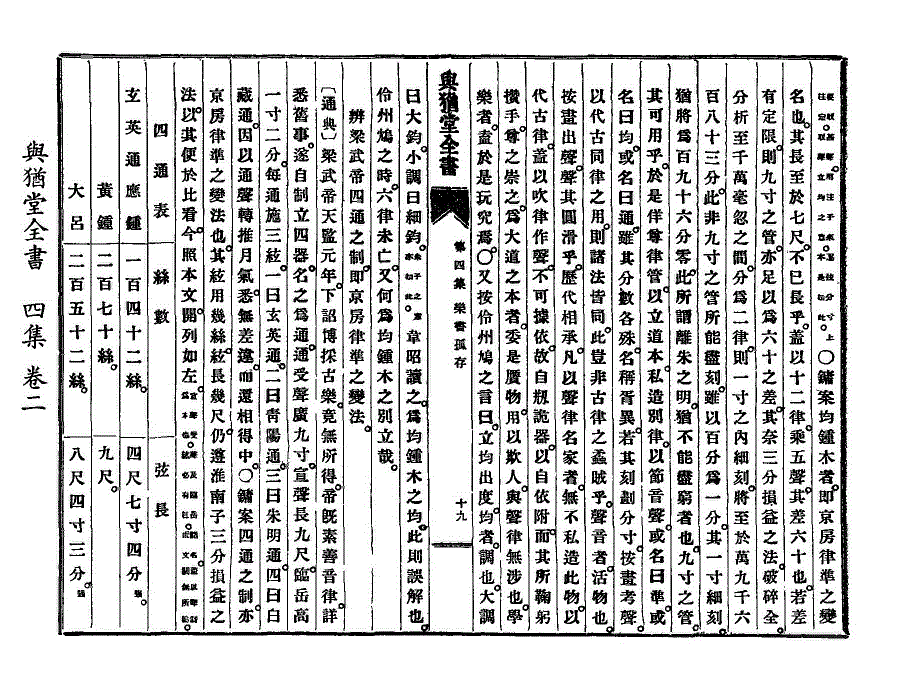 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〇镛案均钟木者。即京房律准之变名也。其长至于七尺。不已长乎。盖以十二律。乘五声。其差六十也。若差有定限。则九寸之管。亦足以为六十之差。其奈三分损益之法。破碎全。分析至千万毫忽之间。分为二律。则一寸之内细刻。将至于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此非九寸之管所能尽刻。虽以百分为一分。其一寸细刻。犹将为百九十六分零。此所谓离朱之明。犹不能尽穷者也。九寸之管。其可用乎。于是佯尊律管。以立道本。私造别律。以节音声。或名曰准。或名曰均。或名曰通。虽其分数各殊。名称胥异。若其刻划分寸。按画考声。以代古同律之用。则诸法皆同。此岂非古律之蟊贼乎。声音者。活物也。按画出声。声其圆滑乎。历代相承。凡以声律名家者。无不私造此物。以代古律。盖以吹律作声。不可据依。故自创诡器。以自依附。而其所鞠躬攒手。尊之崇之。为大道之本者。委是赝物。用以欺人。与声律无涉也。学乐者。盍于是玩究焉。〇又按伶州鸠之言曰。立均出度。均者。调也。大调曰大钧。小调曰细钧。(朱子之意亦如此。)韦昭读之。为均钟木之均。此则误解也。伶州鸩(一作鸠)之时。六律未亡。又何为均钟木之别立哉。
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〇镛案均钟木者。即京房律准之变名也。其长至于七尺。不已长乎。盖以十二律。乘五声。其差六十也。若差有定限。则九寸之管。亦足以为六十之差。其奈三分损益之法。破碎全。分析至千万毫忽之间。分为二律。则一寸之内细刻。将至于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此非九寸之管所能尽刻。虽以百分为一分。其一寸细刻。犹将为百九十六分零。此所谓离朱之明。犹不能尽穷者也。九寸之管。其可用乎。于是佯尊律管。以立道本。私造别律。以节音声。或名曰准。或名曰均。或名曰通。虽其分数各殊。名称胥异。若其刻划分寸。按画考声。以代古同律之用。则诸法皆同。此岂非古律之蟊贼乎。声音者。活物也。按画出声。声其圆滑乎。历代相承。凡以声律名家者。无不私造此物。以代古律。盖以吹律作声。不可据依。故自创诡器。以自依附。而其所鞠躬攒手。尊之崇之。为大道之本者。委是赝物。用以欺人。与声律无涉也。学乐者。盍于是玩究焉。〇又按伶州鸠之言曰。立均出度。均者。调也。大调曰大钧。小调曰细钧。(朱子之意亦如此。)韦昭读之。为均钟木之均。此则误解也。伶州鸩(一作鸠)之时。六律未亡。又何为均钟木之别立哉。辨梁武帝四通之制。即京房律准之变法。
《通典》梁武帝天监元年。下诏博采古乐。竟无所得。帝既素善音律。详悉旧事。遂自制立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阳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〇镛案四通之制。亦京房律准之变法也。其弦用几丝。弦长几尺。仍遵淮南子三分损益之法。以其便于比看。今照本文。开列如左。宣声受声及临岳诸名。盖以琴制为本也。纮(一作弦)必有柱。而文阙无所论。
四通表丝数弦长
玄英通应钟一百四十二丝四尺七寸四分(强)
玄英通黄钟二百七十丝九尺
玄英通大吕二百五十二丝八尺四寸三分(强)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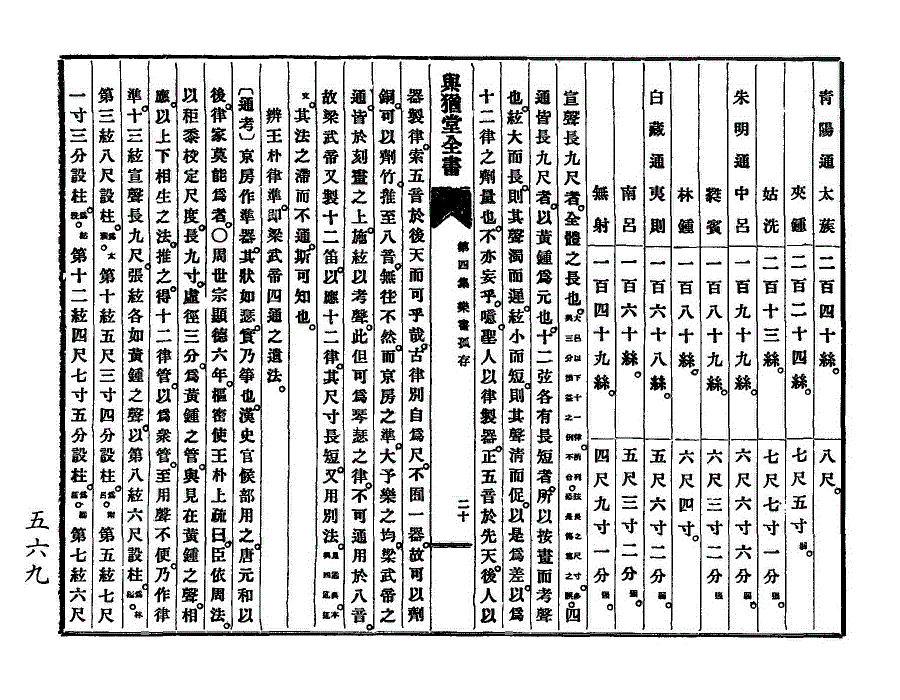 青阳通太蔟二百四十丝八尺
青阳通太蔟二百四十丝八尺青阳通夹钟二百二十四丝七尺五寸(弱)
青阳通姑洗二百十三丝七尺七寸一分(强)
朱明通中吕一百九十九丝六尺六寸六分(弱)
朱明通蕤宾一百八十九丝六尺三寸二分(强)
朱明通林钟一百八十丝六尺四寸
白藏通夷则一百六十八丝五尺六寸二分(弱)
白藏通南吕一百六十丝五尺三寸二分(强)
白藏通无射一百四十九丝四尺九寸一分(强)
宣声长九尺者。全体之长也。(大吕以下十一律。所列弦长之尺寸。多与三分损益之例不合。恐是传写之误。)四通皆长九尺者。以黄钟为元也。十二弦(一作弦)各有长短者。所以按画而考声也。弦大而长。则其声浊而迟。弦小而短。则其声清而促。以是为差。以为十二律之剂量也。不亦妄乎。噫。圣人以律制器。正五音于先天。后人以器制律。索五音于后天而可乎哉。古律别自为尺。不囿一器。故可以剂铜。可以剂竹。推至八音。无往不然。而京房之准。大予乐之均。梁武帝之通。皆于刻画之上。施弦以考声。此但可为琴瑟之律。不可通用于八音。故梁武帝又制十二笛。以应十二律。其尺寸长短。又用别法。(见通典。本与四通连文。)其法之滞而不通。斯可知也。
辨王朴律准。即梁武帝四通之遗法。
《通考》京房作准器。其状如瑟。实乃筝也。汉史官候部用之。唐元和以后。律家莫能为者。〇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0H 页
 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주-D001清声。 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节)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于太常寺。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从之。〇镛案京房律准之制。后世无传。王朴律准。乃其自创。非京房旧法。然宣声之长。至于九尺。但可为琴律。不可为钟磬管籥之通。律乃梁武帝四通之遗法。朱子取之。为琴律者也。(详见琴律说。)比之陈仲孺细刻之准。虽若简捷。以之代六律而正五音。非所论也。盖自京房以来。每以十二律。寓之于弦数。其有济乎弦数者。所以应五声。非所以应六律也。(见下篇。)
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주-D001清声。 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节)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于太常寺。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从之。〇镛案京房律准之制。后世无传。王朴律准。乃其自创。非京房旧法。然宣声之长。至于九尺。但可为琴律。不可为钟磬管籥之通。律乃梁武帝四通之遗法。朱子取之。为琴律者也。(详见琴律说。)比之陈仲孺细刻之准。虽若简捷。以之代六律而正五音。非所论也。盖自京房以来。每以十二律。寓之于弦数。其有济乎弦数者。所以应五声。非所以应六律也。(见下篇。)《通考》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和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西京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〇镛案律准之法。下逮王朴和岘。无不讲用。虽其尺寸长短。微有出入。若其刻划分数。按画考声。则诸法皆同。此非古律之蟊贼乎。〇又按万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所谓水尺。亦律准之类也。已见前编。(千八声之条。)
辨五钟有哑。本由十二律还宫之法。
《通典》唐太宗时。太常卿祖孝孙等曰。旋宫之乐。久丧。汉章帝建初三年。鲍邺始请用之。顺帝阳嘉二年。复废累代。会黄钟一均。变极七音。则五钟废而不击。反谓之哑钟。祖孝孙始为旋宫之法。造十二和乐。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调。(通考云。太宗召张文牧令与祖孝孙。参定雅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有其七。馀五者。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由此观之。近代惟用其七。岂有他哉。蔽于不用十二律。而溺于二变故也。然则二变。不可用于钟律。明矣。)〇镛案哑钟有五者。以还宫也。还宫之法。必至于八十四调。虽郊庙大祭。不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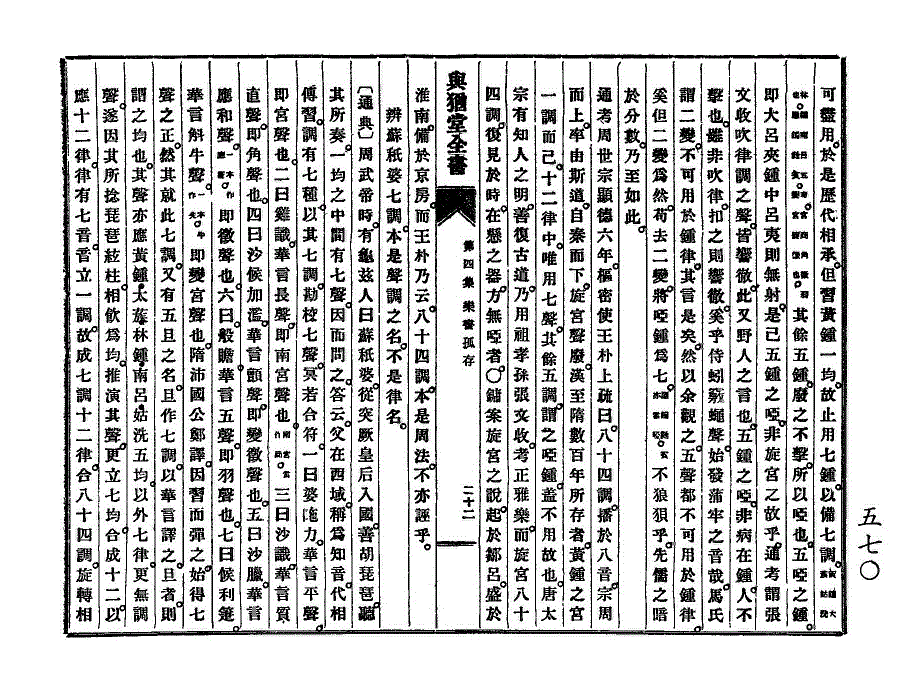 可尽用。于是历代相承。但习黄钟一均。故止用七钟。以备七调。(黄钟大蔟姑洗林钟南吕五者。宫商角徵羽也。应钟蕤宾。变宫变徵也。)其馀五钟。废之不击。所以哑也。五哑之钟。即大吕夹钟中吕夷则无射。是已五钟之哑。非旋宫之故乎。通考谓张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此又野人之言也。五钟之哑。非病在钟。人不击也。虽非吹律。扣之则响彻。奚乎侍(侍乎)蚓窍蝇声。始发蒲牢之音哉。马氏谓二变。不可用于钟律。其言是矣。然以余观之。五声都不可用于钟律。奚但二变为然。苟去二变。将哑钟为七。(应钟蕤宾亦当哑。)不狼狈乎。先儒之暗于分数。乃至如此。
可尽用。于是历代相承。但习黄钟一均。故止用七钟。以备七调。(黄钟大蔟姑洗林钟南吕五者。宫商角徵羽也。应钟蕤宾。变宫变徵也。)其馀五钟。废之不击。所以哑也。五哑之钟。即大吕夹钟中吕夷则无射。是已五钟之哑。非旋宫之故乎。通考谓张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此又野人之言也。五钟之哑。非病在钟。人不击也。虽非吹律。扣之则响彻。奚乎侍(侍乎)蚓窍蝇声。始发蒲牢之音哉。马氏谓二变。不可用于钟律。其言是矣。然以余观之。五声都不可用于钟律。奚但二变为然。苟去二变。将哑钟为七。(应钟蕤宾亦当哑。)不狼狈乎。先儒之暗于分数。乃至如此。《通考》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八十四调。播于八音。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汉至隋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〇镛案旋宫之说。起于邹吕。盛于淮南。备于京房。而王朴乃云。八十四调。本是周法。不亦诬乎。
辨苏秖(一作祗)婆七调。本是声调之名。不是律名。
《通典》周武帝时。有龟玆人曰苏秖(一作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宫声也。(南宫当作商。)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候加滥。华言颤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一本作应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候利箑。华言斛牛声。(一本牛作先。)即变宫声也。隋沛国公郑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之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蔟、林钟、南吕、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无调声。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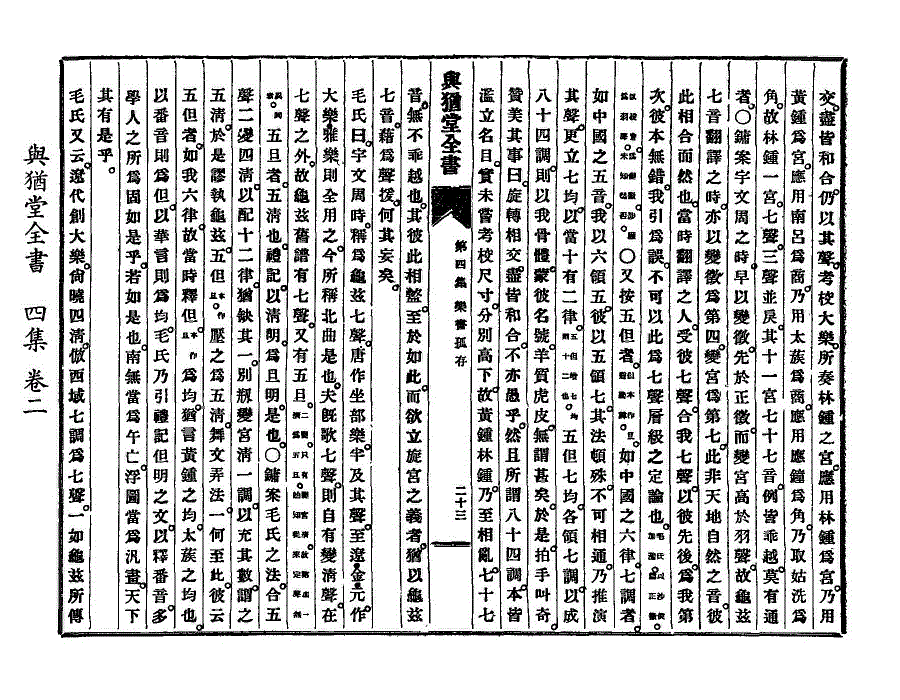 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蔟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〇镛案宇文周之时。早以变徵。先于正徵。而变宫高于羽声。故龟玆七音翻译之时。亦以变徵为第四。变宫为第七。此非天地自然之音。彼此相合而然也。当时翻译之人。受彼七声。合我七声。以彼先后。为我第次。彼本无错。我引为误。不可以此为七声层级之定论也。毛氏以沙侯加滥。为正徵。以般赡。为变徵。涉(一作沙)腊为羽声。未知然否。 〇又按五但者。(但本作旦。避国讳。)如中国之六律。七调者。如中国之五音。我以六领五。彼以五领七。其法顿殊。不可相通。乃推演其声。更立七均。以当十有二律。(五但增七均则十二也。)五但七均。各领七调。以成八十四调。则以我骨体。蒙彼名号。羊质虎皮。无谓甚矣。于是。拍手叫奇。赞美其事曰。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不亦愚乎。然且所谓八十四调。本皆滥立名目。实未尝考校尺寸。分别高下。故黄钟林钟。乃至相乱。七十七音。无不乖越也。其彼此相盭。至于如此。而欲立旋宫之义者。犹以龟玆七音。藉为声援。何其妄矣。
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蔟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〇镛案宇文周之时。早以变徵。先于正徵。而变宫高于羽声。故龟玆七音翻译之时。亦以变徵为第四。变宫为第七。此非天地自然之音。彼此相合而然也。当时翻译之人。受彼七声。合我七声。以彼先后。为我第次。彼本无错。我引为误。不可以此为七声层级之定论也。毛氏以沙侯加滥。为正徵。以般赡。为变徵。涉(一作沙)腊为羽声。未知然否。 〇又按五但者。(但本作旦。避国讳。)如中国之六律。七调者。如中国之五音。我以六领五。彼以五领七。其法顿殊。不可相通。乃推演其声。更立七均。以当十有二律。(五但增七均则十二也。)五但七均。各领七调。以成八十四调。则以我骨体。蒙彼名号。羊质虎皮。无谓甚矣。于是。拍手叫奇。赞美其事曰。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不亦愚乎。然且所谓八十四调。本皆滥立名目。实未尝考校尺寸。分别高下。故黄钟林钟。乃至相乱。七十七音。无不乖越也。其彼此相盭。至于如此。而欲立旋宫之义者。犹以龟玆七音。藉为声援。何其妄矣。毛氏曰。宇文周时。称为龟玆七声。唐作坐部乐。半及其声。至辽、金、元。作大乐、雅乐则全用之。今所称北曲是也。夫既歌七声。则自有变清声。在七声之外。故龟玆旧谱有七声。又有五旦。(二变。只有变宫清。故第加一清为五旦。始知从来定声无异同者。)五旦者。五清也。礼记。以清明。为旦明。是也。〇镛案毛氏之法。合五声二变四清。以配十二律。犹缺其一。别创变宫清一调。以充其数。谓之五清。于是谬执龟玆。五但(本作旦。)压之为五清。舞文弄法。一何至此。彼云五但者。如我六律。故当时释但。(本作旦)为均。犹言黄钟之均。太蔟之均也。以番音则为但。以华言则为均。毛氏乃引礼记但明之文。以释番音。多学人之所为固如是乎。若如是也。南无当为午亡。浮图当为汎画。天下其有是乎。
毛氏又云。辽代创大乐。尚晓四清。仿西域七调为七声。一如龟玆所传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1L 页
 旧律。至于清声。则独能去一变清。但取五声之四清。而隶以二十八调。其曰婆陀力旦。即宫清也。故其所隶七调。皆称宫。(如正宫黄钟宫类。)曰鸡识旦。即商清也。故所隶七调。皆称商。(如双调林钟商调类。)曰沙识旦。即角清也。故其所隶七调。皆称角。(如大食角高大食角类。)曰沙侯加滥旦。即徵清也。故所隶七调。皆称徵。(如般涉调。高般涉调类。般涉。华言徵也。)虽其所为调。不解何等。然能于旧谱五旦中。独去一旦。为四清。此则隋唐后立乐所不及者。况其所去者。适是羽清以羽无清声也。不知当时何以便见及此。〇镛案辽之七调。即龟玆七调。名实未变。数目不改。何得翻弄如是。龟玆七调。止有五声二变。本无四清。安得以婆陀力但。为宫清。鸡识但。为商清乎。然且龟玆只有五但。本无七但。婆陀力鸡识沙识之等。原是调名不是但名。辽人谬执七调。以为七但。毛氏不知驳正。乃欲依此以自立。不已窘乎。七但除四清。则馀者三声。又为何清。不知所以处此也。
旧律。至于清声。则独能去一变清。但取五声之四清。而隶以二十八调。其曰婆陀力旦。即宫清也。故其所隶七调。皆称宫。(如正宫黄钟宫类。)曰鸡识旦。即商清也。故所隶七调。皆称商。(如双调林钟商调类。)曰沙识旦。即角清也。故其所隶七调。皆称角。(如大食角高大食角类。)曰沙侯加滥旦。即徵清也。故所隶七调。皆称徵。(如般涉调。高般涉调类。般涉。华言徵也。)虽其所为调。不解何等。然能于旧谱五旦中。独去一旦。为四清。此则隋唐后立乐所不及者。况其所去者。适是羽清以羽无清声也。不知当时何以便见及此。〇镛案辽之七调。即龟玆七调。名实未变。数目不改。何得翻弄如是。龟玆七调。止有五声二变。本无四清。安得以婆陀力但。为宫清。鸡识但。为商清乎。然且龟玆只有五但。本无七但。婆陀力鸡识沙识之等。原是调名不是但名。辽人谬执七调。以为七但。毛氏不知驳正。乃欲依此以自立。不已窘乎。七但除四清。则馀者三声。又为何清。不知所以处此也。谪居苦无书籍。溯考乐制。下逮唐、宋。粗有纂述。元、明以来。名儒硕学开发之论。涤荡之制。一无所考。顾玆蒙陋。将谁启迪。惟近世毛氏所著乐论数种。适携到此。此公聪明该洽。虽称绝世。其立论立制。不据正理。不循实迹。纬家杂法。未尽清脱。史籍旧文。好自翻弄。虽文锋豪快。未敢尽信。况其乐学。坚守相生之谬法。益创旋宫之乖例。尤以六律。认作五声。每演宫商角徵。以充钟吕蕤洗。其言益辨而其术益荒。是说若行。既亡之乐。尤当澌灭。顾以谫劣。安敢婴锋。特自记其所以起疑之端。以俟知者。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二)
驳
驳十二律管围皆九分。(以下乐本解说。)
毛云。汉志云。黄钟林钟太蔟。为天地人三律之始。必得其正。夫所谓必得其正者。谓以全寸全分为度。而并无空积忽微之得参其间也。今但一人律而径无全分。必积之忽微而后。可以为围法。则其说废矣。是径三围九。凡律尽然。〇镛案古不吹律。其径围阔狭。都不必争。然行遇不公之说。亦不得不辨。夫径一围三者。六觚之算数也。以之算圆。则围九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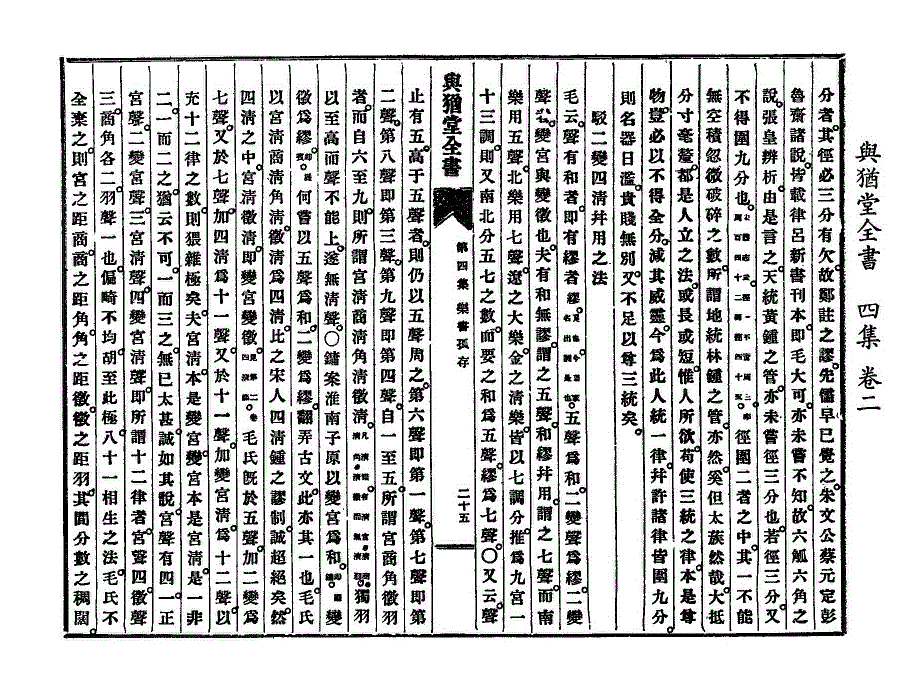 分者。其径必三分有欠(一作奇)。故郑注之谬。先儒早已觉之。朱文公蔡元定彭鲁斋诸说。皆载律吕新书刊本。即毛大可。亦未尝不知。故六觚六角之说。张皇辨析。由是言之。天统黄钟之管。亦未尝径三分也。若径三分。又不得围九分也。(宋历志云。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径围二者之中。其一不能无空积忽微破碎之数。所谓地统林钟之管。亦然。奚但太蔟然哉。大抵分寸毫釐。都是人立之法。或长或短。惟人所欲。苟使三统之律。本是尊物。岂必以不得全分。减其威灵。今为此人统一律。并许诸律皆围九分。则名器日滥。贵贱无别。又不足以尊三统矣。
分者。其径必三分有欠(一作奇)。故郑注之谬。先儒早已觉之。朱文公蔡元定彭鲁斋诸说。皆载律吕新书刊本。即毛大可。亦未尝不知。故六觚六角之说。张皇辨析。由是言之。天统黄钟之管。亦未尝径三分也。若径三分。又不得围九分也。(宋历志云。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径围二者之中。其一不能无空积忽微破碎之数。所谓地统林钟之管。亦然。奚但太蔟然哉。大抵分寸毫釐。都是人立之法。或长或短。惟人所欲。苟使三统之律。本是尊物。岂必以不得全分。减其威灵。今为此人统一律。并许诸律皆围九分。则名器日滥。贵贱无别。又不足以尊三统矣。驳二变四清并用之法
毛云。声有和者。即有缪者。(缪。戾也。今乐家名出调是也。)五声为和。二变声为缪。二变声者。变宫与变徵也。夫有和无谬(一作缪)。谓之五声。和缪并用。谓之七声。而南乐用五声。北乐用七声。辽之大乐。金之清乐。皆以七调分。推为九宫一十三调。则又南北分五七之数。而要之和为五声。缪为七声。〇又云。声止有五。高于五声者。则仍以五声周之。第六声即第一声。第七声即第二声。第八声即第三声。第九声即第四声。自一至五。所谓宫商角徵羽者。而自六至九。则所谓宫清商清角清徵清。(凡清乐。有清宫、清商、清角、清徵而无清羽。)独羽以至高而声不能上。遂无清声。〇镛案淮南子原以变宫为和。(即应钟。)变徵为缪。(即蕤宾。)何尝以五声为和。二变为缪。翻弄古文。此亦其一也。毛氏以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为四清。比之宋人四清钟之谬制。诚超绝矣。然四清之中。宫清徵清。即变宫变徵。(见第二卷四清条。)毛氏既于五声。加二变为七声。又于七声。加四清为十一声。又于十一声。加变宫清。为十二声。以充十二律之数。则猥杂极矣。夫宫清。本是变宫。变宫本是宫清。是一非二。一而二之。犹云不可。一而三之。无已太甚。诚如其说。宫声有四。一正宫声。二变宫声。三宫清声。四变宫清声。即所谓十二律者。宫声四。徵声三。商角各二。羽声一也。偏畸不均。胡至此极。八十一相生之法。毛氏不全弃之。则宫之距商。商之距角。角之距徵。徵之距羽。其间分数之稠阔。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2L 页
 大抵相近。(如八十一、七十二、六十四之类。)何得宫商之间。插此三律。(变宫。清宫。变宫清。)夫十有二律。本应天地四时。(周礼文)磊磊落落。确然并列。何苦为此东贷西乞。仰捃俯拾。崎艰苟且。以充此十有二数哉。夫六律自六律。五声自五声。故舜以六律和五声。孟子以六律正五音。天地恢恢。二者并容。何苦锤破六律。合之五声。然后快于心哉。秦、汉以来二千馀年。凡言声律之事者。万口同声。以毁六律。毛君何为而助力也。且观毛氏之说。以五声四清。谓之九声。则九声之内。原有二变。又何以兼执两名。苟意双用乎。
大抵相近。(如八十一、七十二、六十四之类。)何得宫商之间。插此三律。(变宫。清宫。变宫清。)夫十有二律。本应天地四时。(周礼文)磊磊落落。确然并列。何苦为此东贷西乞。仰捃俯拾。崎艰苟且。以充此十有二数哉。夫六律自六律。五声自五声。故舜以六律和五声。孟子以六律正五音。天地恢恢。二者并容。何苦锤破六律。合之五声。然后快于心哉。秦、汉以来二千馀年。凡言声律之事者。万口同声。以毁六律。毛君何为而助力也。且观毛氏之说。以五声四清。谓之九声。则九声之内。原有二变。又何以兼执两名。苟意双用乎。驳蕤宾以上。为五声二变。
삽화 새창열기
毛云。吕氏春秋。列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七律为上层。即七声也。列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五律为下层。即五清也。上律生下律。谓之正生清。下律生上律。谓之清生正。〇镛案以阴阳之定位。则当以六律为上层。六吕为下层。以长短之序次。则当以中吕以上。为上层。蕤宾以下。为下层。吕氏乃以蕤宾以上。为上层者。一阴一阳。下上相生。生至蕤宾。不得不上生阴吕。(义见前。)而夷则无射。不得不下生。故吕法如彼。毛氏乃欲据此谬义。快将十二之数。截七截五。或弃或用。以立其乖拗之法。其可得乎。〇从来说相生之法者。皆以黄钟为一元。大本十一律。皆于是乎受生。今毛氏之法。黄钟、大吕双立为祖。两下为孙。黄钟之派。七传至蕤宾而穷。大吕之派。五传至中吕而穷。天下有如是相生乎。荒唐甚矣。(其二调以下。至七调相生之图。益以狂乱。今并删之。)〇总之。物各有主。名生于实。挤其主而夺之物。谓之贼。违其实而冒其名。谓之赝。夫上下相生之法。十二还宫之术。吕不韦、刘安。其主人也。而司马迁、刘歆、班固、蔡邕、郑玄之等。其众主人也。籍历俱存。扃鐍犹完。毛氏猝入赵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3H 页
 壁。遍插赤帜。抑何故也。彼所上生。改作下生。彼所方生。改作已穷。(即蕤宾。)彼所为角。我以为徵。(即姑洗。)彼用为正。我以为清。翻倒改换。眼鼻都幻。而天然号之曰此相生法。此旋宫法。天下其有是乎。夫相生旋宫之说。本出周公所作。或系孔子所言。则击彼谬义。立我正旨。亦儒者之恒务。今也不然。邹、吕、刘、马之等。创建基业。自作祖宗。而眇末后学。操戈而入其室曰。此法非也。吾法是相生之正脉。此图误也。吾图是旋宫之妙解。非狂夫乎。然且旋宫之说。本戴同礼。苟欲正之。宜据周礼。奉为关石。则词严义正。谁敢侮矣。今也二至奏乐之经。束之高阁。且置一边。稍变刘吕之法。犹蒙刘、吕之幂。而俨冒旋宫之名。则上而不得为周礼之忠臣。下而不得为刘、吕之纪仆。天下何所当乎。
壁。遍插赤帜。抑何故也。彼所上生。改作下生。彼所方生。改作已穷。(即蕤宾。)彼所为角。我以为徵。(即姑洗。)彼用为正。我以为清。翻倒改换。眼鼻都幻。而天然号之曰此相生法。此旋宫法。天下其有是乎。夫相生旋宫之说。本出周公所作。或系孔子所言。则击彼谬义。立我正旨。亦儒者之恒务。今也不然。邹、吕、刘、马之等。创建基业。自作祖宗。而眇末后学。操戈而入其室曰。此法非也。吾法是相生之正脉。此图误也。吾图是旋宫之妙解。非狂夫乎。然且旋宫之说。本戴同礼。苟欲正之。宜据周礼。奉为关石。则词严义正。谁敢侮矣。今也二至奏乐之经。束之高阁。且置一边。稍变刘吕之法。犹蒙刘、吕之幂。而俨冒旋宫之名。则上而不得为周礼之忠臣。下而不得为刘、吕之纪仆。天下何所当乎。驳四上尺工六。以定古乐。
毛云。笛色四上尺工六五字之外。又有高侐高仩高伬高仜四高字也。(无高𠆾字者。以无羽清也。)此九声也。今器色家。犹知以九声立调是也。〇又云。箫篪管笛。一一受准于籥。籥。单箫也。箫穴为四乙上尺工凡六。(句)七声而七声之尽。则第八声即第一声。第九声即第二声。所谓高侐高亿是也。四与高侐。乙与高亿。原是一声。而四乙为本声。侐与亿。即为清声。推之而至于上尺工凡六。皆然。是籥箫五器。凡隔八穴。无不前后同声。复还其始者。〇镛案四上尺工六者。乐工之私记也。其法莫详于朱子琴律说及蔡元定燕乐谱。今取二文。录之在左。〇乐亡久矣。乐工之所传习。皆以汉唐宋儒者之说。为诀为谱。非伦夔一脉。传旷传襄。绵绵不绝。以至今日也。则四上尺工。未必更尊于宋元诸儒之说。毛氏作乐书十馀卷。全戴此物。以为左證。有若吹弹之家。原有单传密付真诠秘诀。犹存三古之遗声者然。得无诈乎。今考四上尺工之源流。殊与毛说不同。此又不可知者。
《沈括笔谈》据唐人琵琶录。以为调琴之法。须先以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祉。祉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〇朱子曰。以合声定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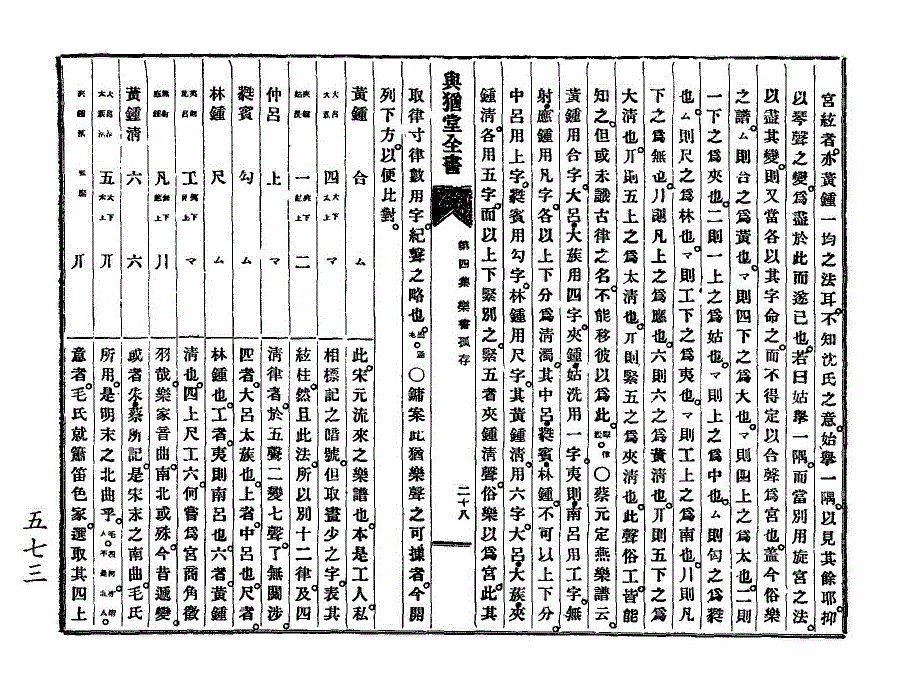 宫弦者。亦黄钟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始举一隅。以见其馀耶。抑以琴声之变。为尽于此而遂已也。若曰姑举一隅。而当别用旋宫之法。以尽其变。则又当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声为宫也。盖今俗乐之谱。(厶)则合之为黄也。(マ)则四下之为大也。(マ)则四上之为太也。二则一下之为夹也。二则一上之为姑也。(マ)则上之为中也。(厶)则丐(一作勾)之为蕤也。(厶)则尺之为林也。(マ)则工下之为夷也。(マ)则工上之为南也。
宫弦者。亦黄钟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始举一隅。以见其馀耶。抑以琴声之变。为尽于此而遂已也。若曰姑举一隅。而当别用旋宫之法。以尽其变。则又当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声为宫也。盖今俗乐之谱。(厶)则合之为黄也。(マ)则四下之为大也。(マ)则四上之为太也。二则一下之为夹也。二则一上之为姑也。(マ)则上之为中也。(厶)则丐(一作勾)之为蕤也。(厶)则尺之为林也。(マ)则工下之为夷也。(マ)则工上之为南也。삽화 새창열기
此。宋元流来之乐谱也。本是工人。私相标记之暗号。但取画少之字。表其弦柱。然且此法。所以别十二律。及四清律者。于五声二变七声。了无关涉。四者。大吕太蔟也。上者。中吕也。尺者。林钟也。工者。夷则南吕也。六者。黄钟清也。四上尺工六。何尝为宫商角徵羽哉。乐家音曲。南北或殊。今昔递变。或者朱、蔡所记。是宋末之南曲。毛氏所用。是明末之北曲乎。(毛西河。亦南人。不是北人。)意者。毛氏就箫笛色家。选取其四上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4H 页
 尺工六。(句)五字以为五声之标号。又取凡乙二字。以为二变之标号也。(乙者。一也。琴说所云。一下一上。乃乙下乙上也。)不然。亦今昔有变耳。〇总之。笛色之家。有四上尺工六。又有高侐高仩高伬高仜。则五正四清九声而已。箫色之家。有四上尺工六。又有乙凡二字。则五正二变七声而已。既计二变。谓之七声。又计四清。谓之十一声。又立变清。谓之十二声。则古今天下。万无此事。毛谓箫色家。有高侐高亿。盖四者。大吕太蔟之名。乙者。夹钟姑洗之名。高侐高亿者。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之清声也。宋代四清之钟。或自黄钟。取至夹钟。(子丑寅卯律。)或自大吕。取至姑洗。(丑寅卯辰律。)其自大吕。取至姑洗者。以黄钟至尊。虽其子声。犹不敢屈之相役。故取自大吕。以立四清也。由是观之。所谓箫色家之高侐高亿者。即大吕太蔟之清。(二者。皆高侐。)夹钟姑洗之清。(二者。皆高亿。)万万非宫清、变宫清之标记也。(毛以高侐高亿。为宫清。变宫清。)大抵汉唐以降。凡刻画分寸。以别声调者。若京房之准。大予之均。梁武帝之通。下逮王朴知岘之所作。都是十二律之标记。五声二变。何曾梦到。十有二律。以配于五声二变则有之。直以五声二变。别立四上乙凡之名。宋元乐谱。必无此迹。毛氏之翻弄那移。可胜言哉。〇凡郊庙雅乐。但用五声。苟欲缛文。宜加二变。至于四清。非燕乐。俗乐。断不可设。虽然。乐家原有四清。在所采用。惟配之律吕。又增旋宫之别法。则必不可者。
尺工六。(句)五字以为五声之标号。又取凡乙二字。以为二变之标号也。(乙者。一也。琴说所云。一下一上。乃乙下乙上也。)不然。亦今昔有变耳。〇总之。笛色之家。有四上尺工六。又有高侐高仩高伬高仜。则五正四清九声而已。箫色之家。有四上尺工六。又有乙凡二字。则五正二变七声而已。既计二变。谓之七声。又计四清。谓之十一声。又立变清。谓之十二声。则古今天下。万无此事。毛谓箫色家。有高侐高亿。盖四者。大吕太蔟之名。乙者。夹钟姑洗之名。高侐高亿者。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之清声也。宋代四清之钟。或自黄钟。取至夹钟。(子丑寅卯律。)或自大吕。取至姑洗。(丑寅卯辰律。)其自大吕。取至姑洗者。以黄钟至尊。虽其子声。犹不敢屈之相役。故取自大吕。以立四清也。由是观之。所谓箫色家之高侐高亿者。即大吕太蔟之清。(二者。皆高侐。)夹钟姑洗之清。(二者。皆高亿。)万万非宫清、变宫清之标记也。(毛以高侐高亿。为宫清。变宫清。)大抵汉唐以降。凡刻画分寸。以别声调者。若京房之准。大予之均。梁武帝之通。下逮王朴知岘之所作。都是十二律之标记。五声二变。何曾梦到。十有二律。以配于五声二变则有之。直以五声二变。别立四上乙凡之名。宋元乐谱。必无此迹。毛氏之翻弄那移。可胜言哉。〇凡郊庙雅乐。但用五声。苟欲缛文。宜加二变。至于四清。非燕乐。俗乐。断不可设。虽然。乐家原有四清。在所采用。惟配之律吕。又增旋宫之别法。则必不可者。驳楚词四上。以證乐谱之四上。
毛云。尝梦先教谕。(毛之父。)执大招一篇。指示曰二八四上。古乐经也。汝知之乎。臣悟而大惊。急取大招。谛视之。二八者。人声也。人声十六。二八十六声也。四上者。笛声也。笛色谱曰四上尺工六。为宫商角徵羽四上宫与商也。其前章曰赵箫倡只是也。〇镛案翻弄古文。于斯极矣。二八者。舞列也。舞者。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鲁众仲之语)故以八人为一列。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也。六佾者。六八四十八也。二八者。二八十六人也。故郑人以女乐二八。赂晋侯。(襄十一。)毛氏曾于论语八佾之注。力主此义。以立服虔之说。今乃急于时用。忽以二八。为人声高下之数。其翻弄为何如者。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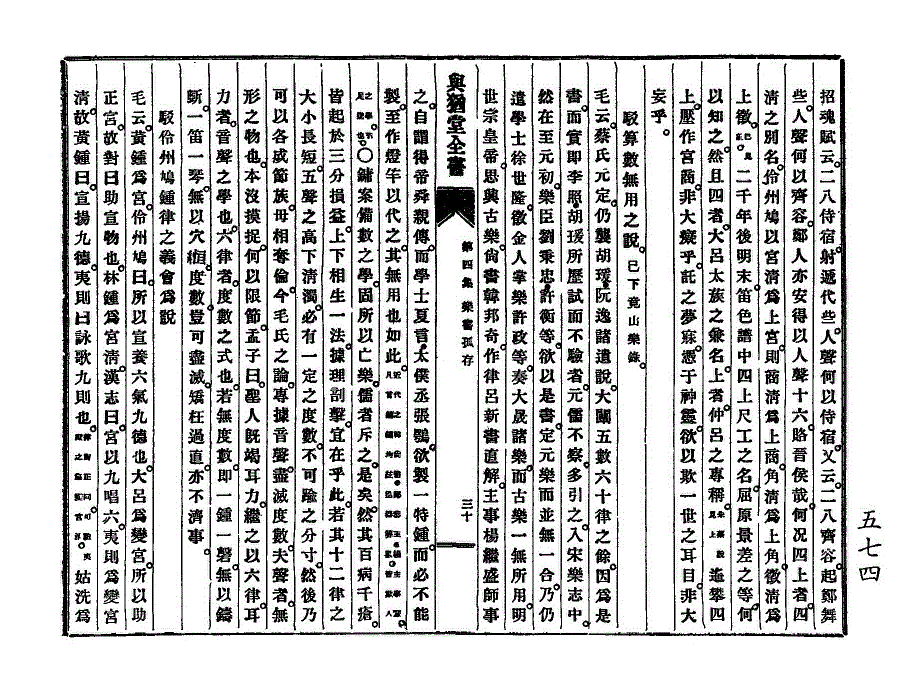 招魂赋云。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人声何以侍宿。又云。二八齐容。起郑舞些。人声何以齐容。郑人亦安得以人声十六。赂晋侯哉。何况四上者。四清之别名。伶州鸠以宫清为上宫。则商清为上商。角清为上角。徵清为上徵。(已见前。)二千年后明末。笛色谱中四上尺工之名。屈原景差之等。何以知之。然且四者。大吕太蔟之兼名。上者。仲吕之专称。(朱蔡说见上)遥攀四上。压作宫商。非大痴乎。托之梦寐。凭于神灵。欲以欺一世之耳目。非大妄乎。
招魂赋云。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人声何以侍宿。又云。二八齐容。起郑舞些。人声何以齐容。郑人亦安得以人声十六。赂晋侯哉。何况四上者。四清之别名。伶州鸠以宫清为上宫。则商清为上商。角清为上角。徵清为上徵。(已见前。)二千年后明末。笛色谱中四上尺工之名。屈原景差之等。何以知之。然且四者。大吕太蔟之兼名。上者。仲吕之专称。(朱蔡说见上)遥攀四上。压作宫商。非大痴乎。托之梦寐。凭于神灵。欲以欺一世之耳目。非大妄乎。驳算数无用之说。(已下竟山乐录。)
毛云。蔡氏元定。仍袭胡瑗、阮逸诸遗说。大阐五数六十律之馀。因为是书。而实即李照、胡瑗所历试而不验者。元儒不察。多引之。入宋乐志中。然在至元初。乐臣刘秉忠、许衡等。欲以是书。定元乐而并无一合。乃仍遣学士徐世隆。徵金人掌乐许政等。奏大晟诸乐。而古乐一无所用。明世宗皇帝。思兴古乐。尚书韩邦奇。作律吕新书直解。主事杨继盛师事之。自谓得帝舜亲传。而学士夏言、太仆丞张鹗。欲制一特钟。而必不能制。至作灯竿以代之。其无用也如此。(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杨主事辈。凡言铸钟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〇镛案备数之学。固所以亡乐。儒者斥之。是矣。然其百病千疮。皆起于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一法。据理剖击。宜在乎此。若其十二律之大小长短。五声之高下清浊。必有一定之度数。不可踰之分寸。然后乃可以各成节族。毋相夺伦。今毛氏之论。专据音声。尽灭度数。夫声者。无形之物也。本没摸捉。何以限节。孟子曰。圣人既竭耳力。继之以六律。耳力者。音声之学也。六律者。度数之式也。若无度数。即一钟一磬。无以铸斲。一笛一琴。无以穴縆。度数。岂可尽灭。矫枉过直。亦不济事。
驳伶州鸠钟律之义주-D001会为说
毛云。黄钟为宫。伶州鸠曰。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大吕为变宫。所以助正宫。故对曰助宣物也。林钟为宫清。汉志曰。宫以九唱六。夷则为变宫清。故黄钟曰。宣扬九德。夷则曰咏歌九则也。(律对正同。可验夷则之为变宫清。)姑洗为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5H 页
 徵。故对曰。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夫飨神燕宾。皆礼事也。则姑洗徵也。中吕为变徵。故宣阳气也。应钟为徵清。故对曰均利器用。俾之应复。盖言洽百物之礼也。〇镛案六律者。经也。五音者。纬也。一律各具一五音。岂得以某律。配某声哉。若用二变。则诸律皆具二变。若用四清。则诸律皆具四清。故经曰。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既不得以八音。分配于六律。何独以五声。胶定于六律乎。六律之不能缺五声。犹其不能离八音。此易知之理。千古梦梦。岂非大惑。伶州鸠所论律吕之义。本与五声无涉。毛氏极意附会。曲成义理。其言皆苟且纰缪。不足多辨。姑略之。
徵。故对曰。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夫飨神燕宾。皆礼事也。则姑洗徵也。中吕为变徵。故宣阳气也。应钟为徵清。故对曰均利器用。俾之应复。盖言洽百物之礼也。〇镛案六律者。经也。五音者。纬也。一律各具一五音。岂得以某律。配某声哉。若用二变。则诸律皆具二变。若用四清。则诸律皆具四清。故经曰。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既不得以八音。分配于六律。何独以五声。胶定于六律乎。六律之不能缺五声。犹其不能离八音。此易知之理。千古梦梦。岂非大惑。伶州鸠所论律吕之义。本与五声无涉。毛氏极意附会。曲成义理。其言皆苟且纰缪。不足多辨。姑略之。驳周自文武后不解七声
毛云。周乐无商调。从来不解。尝以问先臣。先臣曰。周自文武后。便不解七声。故周景王问七律。而伶州鸠以七同七别。妄答之。因以变宫。在宫前一位者。误认作已前之前。遂列变宫。在宫后而宫前一位。名之为商。然而乐工用五声。则宫前一声。每閟不用。此不用者。是变宫而既误为商。则亦误谓不用商。此即无商之所由来也。(若隋唐以后。不用徵调。则十二律配七调。而林钟为无调之首。乃史记以林钟为徵。遂曰无徵调。此皆沿误之最无理者。)〇镛案周自文武后。便不解七声。则周公召公成王康王之等。皆不知七声。作周颂以美成康者。皆不知七声。妄作歌颂。至三千年后。河右老公。始知七声。非悖语乎。景王之时。周道虽衰。钟簴未迁。礼乐未崩。毛公所知。伶州鸠。何以不知。毛于前编。戴州鸠对律之言。以饰其二变四清之律。俄顷之间。又以州鸠七同七列之对。归之妄答。如知其妄。昔何戴之。至于周乐之不用商调。此是周礼经文。周礼者。周公所作。周公误以商声。认作变宫。去之不用。又以变宫。退之于宫后一位。孰谓周公制礼作乐。毛公气粗心热。凡吾欲所发。即天地不分。是尧击尧是舜击舜。虽欲谓之不狂悖。不可得也。然且周乐未尝无商调。故大司乐掌六乐。文之以五声。太师掌六律。文之以五声。何谓无商。特二至奏乐。不用商调。别是一法。岂得以此。谓周乐无商。〇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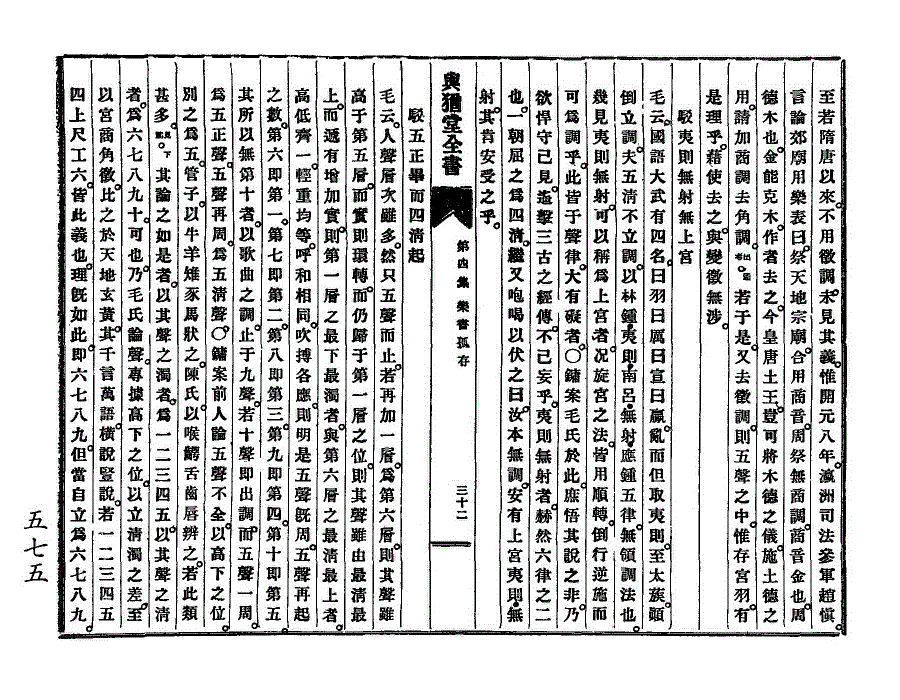 至若隋唐以来。不用徵调。未见其义。惟开元八年。瀛洲司法参军赵慎。言论郊庙用乐表曰。祭天地宗庙。合用商音。周祭无商调。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岂可将木德之仪。施土德之用。请加商调去角调。(出通考。)若于是。又去徵调。则五声之中。惟存宫羽。有是理乎。藉使去之。与变徵无涉。
至若隋唐以来。不用徵调。未见其义。惟开元八年。瀛洲司法参军赵慎。言论郊庙用乐表曰。祭天地宗庙。合用商音。周祭无商调。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岂可将木德之仪。施土德之用。请加商调去角调。(出通考。)若于是。又去徵调。则五声之中。惟存宫羽。有是理乎。藉使去之。与变徵无涉。驳夷则无射无上宫
毛云。国语大武有四名。曰羽曰厉曰宣曰赢。乱而但取夷则。至太蔟。颠倒立调。夫五清不立调。以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五律。无领调法也。几见夷则无射。可以称为上宫者。况旋宫之法。皆用顺转。倒行逆施而可为调乎。此皆于声律。大有碍者。〇镛案毛氏于此。庶悟其说之非。乃欲悍守己见。遥击三古之经传。不已妄乎。夷则无射者。赫然六律之二也。一朝屈之为四清。继又咆喝以伏之曰。汝本无调。安有上宫夷则、无射。其肯安受之乎。
驳五正毕而四清起
毛云。人(一作八)声层次虽多。然只五声而止。若再加一层。无第六层。则其声虽高于第五层。而实则环转。而仍归于第一层之位。则其声虽由最清最上。而递有增加实。则第一层之最下最浊者。与第六层之最清最上者。高低齐一。轻重均等。呼和相同。吹搏各应。则明是五声既周。五声再起之数。第六即第一。第七即第二。第八即第三。第九即第四。第十即第五。其所以无第十者。以歌曲之调。止于九声。若十声即出调。而五声一周。为五正声。五声再周。为五清声。〇镛案前人论五声不全。以高下之位。别之为五。管子。以牛羊雉豕马状之。陈氏。以喉腭舌齿唇(一作唇)辨之。若此类甚多。(见下篇。)其论之如是者。以其声之浊者。为一二三四五。以其声之清者。为六七八九十。可也。乃毛氏论声。专据高下之位。以立清浊之差。至以宫商角徵。比之于天地玄黄。其千言万语。横说竖说。若一二三四五四上尺工六。皆此义也。理既如此。即六七八九。但当自立为六七八九。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6H 页
 安得为一二三四之清声乎。同是牛鸣。则其下者为牛鸣之浊。其高者为牛鸣之清。于理宜然。今牛鸣羊鸣。既不部分。则凡其声益清者。其位益高。何得云一六相应。二七相同乎。据云羽声最高。本无清声。(下文云。)羽声之顶。俨戴四声。犹云羽声最清而可信乎。若云牛呜(一作鸣)羊呜(一作鸣)。声各不同。即豕声马声。宜无异例。马声之独无清。有是理乎。既以高下。别其清浊。乃曰第一层之最下最浊者。与第六层之最高最清者。高低齐一。轻重均等。此是南华老人齐物论中话头。非据实论理之言也。毛氏之意。我知之矣。二变四清。必欲并用。苟以四清。插之五正之间。则二变之名。不可叠设。故遂以四清。黜之在外也。声音者。众耳之所共闻。哀丝细管。高入半空。按节而告诸人曰。此声虽清。本是浊调。彼声虽高。本系下位。微妙之理。非尔所知。斯非欺人语乎。周礼有六变八变九变诸文。乐以一成为一变。故一成既毕。再声继起。三成既毕。四声继起。若是者。羽调既毕。宫调继起也。然再起之宫。此是第二变之第一声。本非第一调之第六声。此是第二变之正宫声。本非第一调之清宫声。那移贸乱。安得如是。然且羽之与宫。碧天黄壤。本不循环。安有两间。苟其相接。即房庶之变羽声。郑译之变宫声。不足为疵。(郑译用龟玆七音。变宫在羽声前。)左絜右度。毛氏之义无所立也。〇总之。古乐五声而已。中古于始作之次。终阕之先。特加二调。谓之二变。及周之末。又加清商清角。总名四清。(韩非子。)亦称四上。(大招文。)而羽声果以最高之故。不立清声。此其大略也。今正其位如左。
安得为一二三四之清声乎。同是牛鸣。则其下者为牛鸣之浊。其高者为牛鸣之清。于理宜然。今牛鸣羊鸣。既不部分。则凡其声益清者。其位益高。何得云一六相应。二七相同乎。据云羽声最高。本无清声。(下文云。)羽声之顶。俨戴四声。犹云羽声最清而可信乎。若云牛呜(一作鸣)羊呜(一作鸣)。声各不同。即豕声马声。宜无异例。马声之独无清。有是理乎。既以高下。别其清浊。乃曰第一层之最下最浊者。与第六层之最高最清者。高低齐一。轻重均等。此是南华老人齐物论中话头。非据实论理之言也。毛氏之意。我知之矣。二变四清。必欲并用。苟以四清。插之五正之间。则二变之名。不可叠设。故遂以四清。黜之在外也。声音者。众耳之所共闻。哀丝细管。高入半空。按节而告诸人曰。此声虽清。本是浊调。彼声虽高。本系下位。微妙之理。非尔所知。斯非欺人语乎。周礼有六变八变九变诸文。乐以一成为一变。故一成既毕。再声继起。三成既毕。四声继起。若是者。羽调既毕。宫调继起也。然再起之宫。此是第二变之第一声。本非第一调之第六声。此是第二变之正宫声。本非第一调之清宫声。那移贸乱。安得如是。然且羽之与宫。碧天黄壤。本不循环。安有两间。苟其相接。即房庶之变羽声。郑译之变宫声。不足为疵。(郑译用龟玆七音。变宫在羽声前。)左絜右度。毛氏之义无所立也。〇总之。古乐五声而已。中古于始作之次。终阕之先。特加二调。谓之二变。及周之末。又加清商清角。总名四清。(韩非子。)亦称四上。(大招文。)而羽声果以最高之故。不立清声。此其大略也。今正其位如左。羽 徵清 徵 角清 角 商清 商 宫清 宫
右所言宫清。即变宫也。徵清。变徵也。
驳宫商之间。徵羽之间。相隔以倍。
毛云。五声层次。相隔均等。如宫商隔一寸。则角徵羽。亦隔一寸。宫商隔二寸。则角徵羽亦隔二寸。稍有参差。即不和。此定理也。乃其事有不尽然者。羽宫相隔。与商角相隔。角徵相隔。俱分寸均等。而宫商之间。与徵羽之间。俱倍之。如有七寸之管于此。第一寸是宫字。乃隔二寸而得商字。则第三寸是商字矣。第四寸是角字。第五寸是徵字。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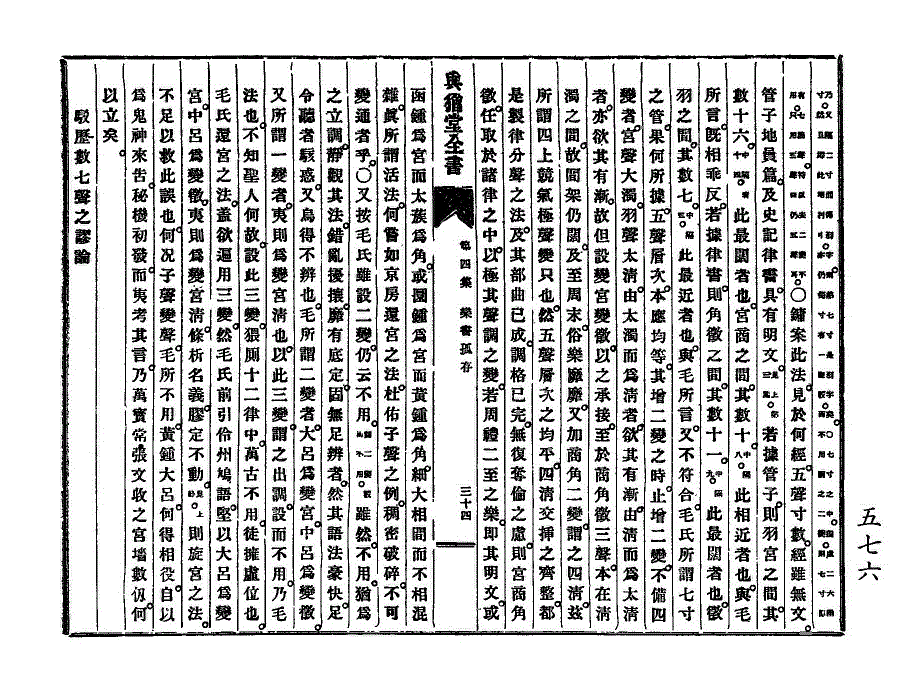 乃又隔二寸而得羽字。则弟(一作第)七寸是羽字矣。〇七寸之中。独虚二六两寸。然且即此两村(一作寸)中。亦仍每寸有一声设。而不用谓之二变。则七寸原有七个声。特以去二变不用。只用五声曰仍五声耳。 〇镛案此法。见于何经。五声寸数。经虽无文。管子地员篇。及史记律书。具有明文。(见上第三篇。)若据管子。则羽宫之间。其数十六。(中隔者十四。)此最阔者也。宫商之间。其数十。(中隔八。)此相近者也。与毛所言。既相乖反。若据律书。则角徵之间。其数十一。(中隔九。)此最阔者也。徵羽之间。其数七。(中隔五。)此最近者也。与毛所言。又不符合。毛氏所谓七寸之管。果何所据。五声层次。本应均等。其增二变之时。止增二变。不备四变者。宫声大浊。羽声太清。由太浊而为清者。欲其有渐。由清而为太清者。亦欲其有渐。故但设变宫变徵。以之承接。至于商角徵三声。本在清浊之间。故间架仍阔。及至周末。俗乐靡靡。又加商角二变。谓之四清。玆所谓四上竞气极声变只也。然五声层次之均平。四清交插之齐整。都是制律分声之法。及其部曲已成。调格已完。无复夺伦之虑。则宫商角徵。任取于诸律之中。以极其声调之变。若周礼二至之乐。即其明文。或函钟为宫而太蔟为角。或圜钟为宫而黄钟为角。细大相间而不相混杂。真所谓活法。何尝如京房还宫之法。杜佑子声之例。稠密破碎。不可变通者乎。〇又按毛氏虽设二变。仍云不用。(谓二变设而不用。)虽然。不用。犹为之立调。静观其法。错乱扰攘。靡有底定。固无足辨者。然其语法豪快。足令听者骇惑。又乌得不辨也。毛所谓二变者。大吕为变宫。中吕为变徵。又所谓一变者。夷则为变宫清也。以此三变。谓之出调。设而不用。乃毛法也。不知圣人何故。设此三变。猥厕十二律中。万古不用。徒拥虚位也。毛氏还宫之法。盖欲遍用三变。然毛氏前引伶州鸠语。坚以大吕为变宫。中吕为变徵。夷则为变宫清。条析名义。胶定不动。(见上条。)则旋宫之法。不足以救此误也。何况子声变声。毛所不用。黄钟大吕。何得相役。自以为鬼神来告。秘机初发。而夷考其言。乃万宝常、张文收之宫墙数仞。何以立矣。
乃又隔二寸而得羽字。则弟(一作第)七寸是羽字矣。〇七寸之中。独虚二六两寸。然且即此两村(一作寸)中。亦仍每寸有一声设。而不用谓之二变。则七寸原有七个声。特以去二变不用。只用五声曰仍五声耳。 〇镛案此法。见于何经。五声寸数。经虽无文。管子地员篇。及史记律书。具有明文。(见上第三篇。)若据管子。则羽宫之间。其数十六。(中隔者十四。)此最阔者也。宫商之间。其数十。(中隔八。)此相近者也。与毛所言。既相乖反。若据律书。则角徵之间。其数十一。(中隔九。)此最阔者也。徵羽之间。其数七。(中隔五。)此最近者也。与毛所言。又不符合。毛氏所谓七寸之管。果何所据。五声层次。本应均等。其增二变之时。止增二变。不备四变者。宫声大浊。羽声太清。由太浊而为清者。欲其有渐。由清而为太清者。亦欲其有渐。故但设变宫变徵。以之承接。至于商角徵三声。本在清浊之间。故间架仍阔。及至周末。俗乐靡靡。又加商角二变。谓之四清。玆所谓四上竞气极声变只也。然五声层次之均平。四清交插之齐整。都是制律分声之法。及其部曲已成。调格已完。无复夺伦之虑。则宫商角徵。任取于诸律之中。以极其声调之变。若周礼二至之乐。即其明文。或函钟为宫而太蔟为角。或圜钟为宫而黄钟为角。细大相间而不相混杂。真所谓活法。何尝如京房还宫之法。杜佑子声之例。稠密破碎。不可变通者乎。〇又按毛氏虽设二变。仍云不用。(谓二变设而不用。)虽然。不用。犹为之立调。静观其法。错乱扰攘。靡有底定。固无足辨者。然其语法豪快。足令听者骇惑。又乌得不辨也。毛所谓二变者。大吕为变宫。中吕为变徵。又所谓一变者。夷则为变宫清也。以此三变。谓之出调。设而不用。乃毛法也。不知圣人何故。设此三变。猥厕十二律中。万古不用。徒拥虚位也。毛氏还宫之法。盖欲遍用三变。然毛氏前引伶州鸠语。坚以大吕为变宫。中吕为变徵。夷则为变宫清。条析名义。胶定不动。(见上条。)则旋宫之法。不足以救此误也。何况子声变声。毛所不用。黄钟大吕。何得相役。自以为鬼神来告。秘机初发。而夷考其言。乃万宝常、张文收之宫墙数仞。何以立矣。驳历数七声之谬论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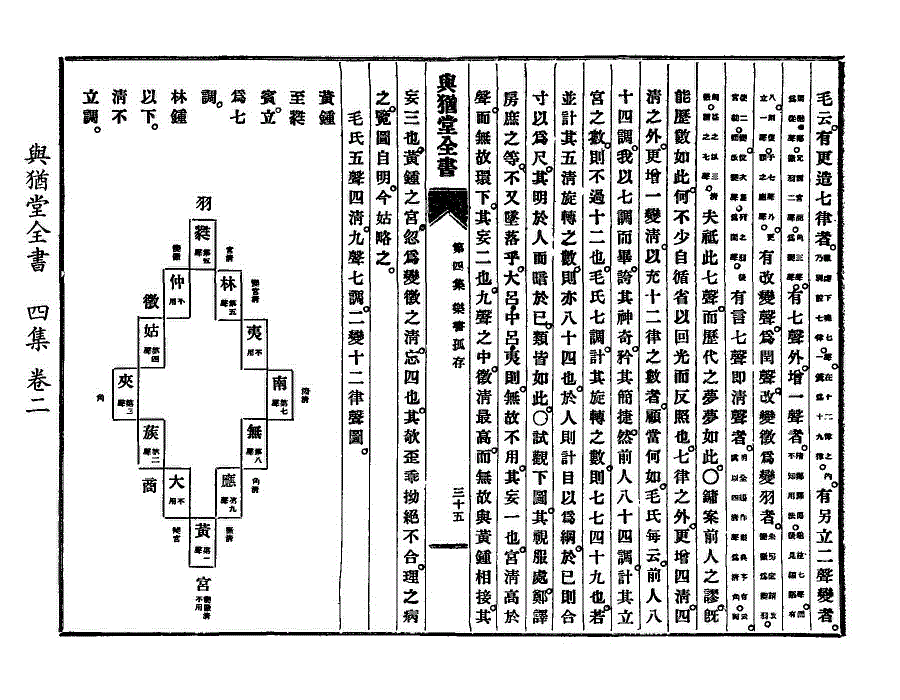 毛云。有更造七律者。(服虔下晓七声。在十二律之内。乃别设七律。一簴为十九律。)有另立二声变者。(马融、郑元谓宫商角三声。为从声。徵羽二声。为变声。)有七声外。增一声者。(隋郑译得龟玆七声。而不知用法。后见编悬有八。则复于七声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有改变声。为闰声。改变徵为变羽者。朱(一作宋)房庶请改变徵为变羽。使二变。位次尽列之羽后宫前。而改变声。为闰声。 有言七声即清声者。(明全赐作乐典序有云。虞以四清声为清角。而周益之以三清徵。谓之七声。)夫祗此七声。而历代之梦梦如此。〇镛案前人之谬。既能历数如此。何不少自循省以回光而反照也。七律之外。更增四清。四清之外。更增一变清。以充十二律之数者。顾当何如。毛氏每云。前人八十四调。我以七调而毕。誇其神奇。矜其简捷。然前人八十四调。计其立宫之数。则不过十二也。毛氏七调。计其旋转之数。则七七四十九也。若并计其五清旋转之数。则亦八十四也。于人则计目以为纲。于己则合寸以为尺。其明于人而暗于己。类皆如此。〇试观下图。其视服处(一作虔)。郑译房庶之等。不又坠落乎。大吕、中吕、夷则。无故不用。其妄一也。宫清高于声。而无故环下。其妄二也。九声之中。徵清最高。而无故与黄钟相接。其妄三也。黄钟之宫。忽为变徵之清。주-D003忘(一作妄)四也。其欹歪乖拗绝不合。理之病之。览图自明。今姑略之。
毛云。有更造七律者。(服虔下晓七声。在十二律之内。乃别设七律。一簴为十九律。)有另立二声变者。(马融、郑元谓宫商角三声。为从声。徵羽二声。为变声。)有七声外。增一声者。(隋郑译得龟玆七声。而不知用法。后见编悬有八。则复于七声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有改变声。为闰声。改变徵为变羽者。朱(一作宋)房庶请改变徵为变羽。使二变。位次尽列之羽后宫前。而改变声。为闰声。 有言七声即清声者。(明全赐作乐典序有云。虞以四清声为清角。而周益之以三清徵。谓之七声。)夫祗此七声。而历代之梦梦如此。〇镛案前人之谬。既能历数如此。何不少自循省以回光而反照也。七律之外。更增四清。四清之外。更增一变清。以充十二律之数者。顾当何如。毛氏每云。前人八十四调。我以七调而毕。誇其神奇。矜其简捷。然前人八十四调。计其立宫之数。则不过十二也。毛氏七调。计其旋转之数。则七七四十九也。若并计其五清旋转之数。则亦八十四也。于人则计目以为纲。于己则合寸以为尺。其明于人而暗于己。类皆如此。〇试观下图。其视服处(一作虔)。郑译房庶之等。不又坠落乎。大吕、中吕、夷则。无故不用。其妄一也。宫清高于声。而无故环下。其妄二也。九声之中。徵清最高。而无故与黄钟相接。其妄三也。黄钟之宫。忽为变徵之清。주-D003忘(一作妄)四也。其欹歪乖拗绝不合。理之病之。览图自明。今姑略之。毛氏五声四清。九声七调。二变十二律声(一作全)图。
삽화 새창열기
第四集乐集第二卷○乐书孤存 第 5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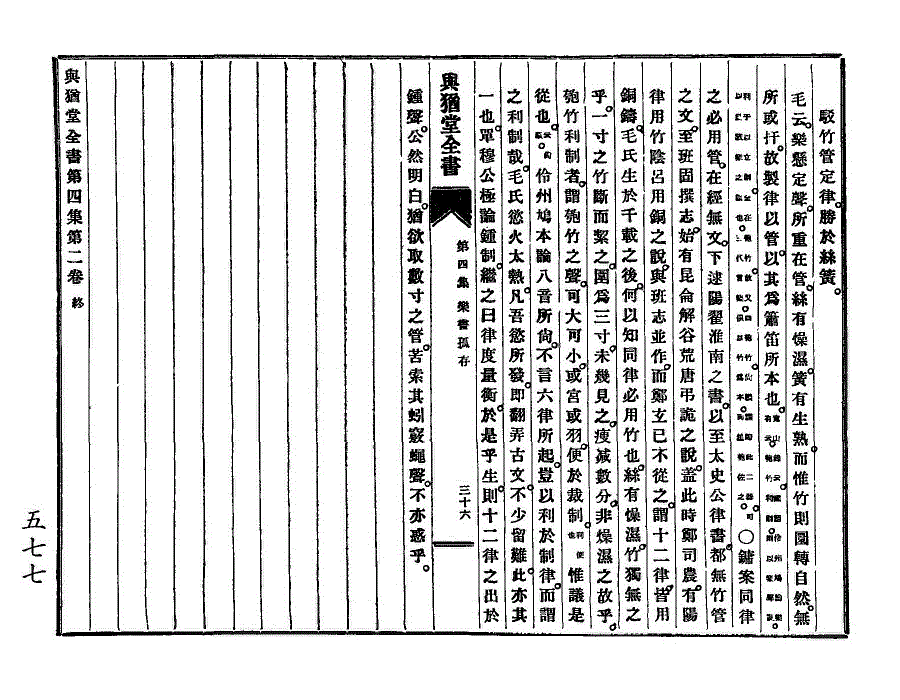 驳竹管定律。胜于丝簧。
驳竹管定律。胜于丝簧。毛云。乐悬定声。所重在管。丝有燥湿。簧有生熟。而惟竹则圜转自然。无所或捍。故制律以管。以其为箫笛所本也。(竟山录云。国语伶州鸠论乐有云。匏竹利制。则以乐声调。利于以立制。全在匏竹。故又曰匏竹。尚议谓即此二器。可以为议乐之制也。三代言乐。俱以竹为本。而笙匏佐之。)〇镛案同律之必用管。在经无文。下逮阳翟淮南之书。以至太史公律书。都无竹管之文。至班固撰志。始有昆仑解谷荒唐吊诡之说。盖此时郑司农。有阳律用竹阴吕用铜之说。与班志并作。而郑玄已不从之。谓十二律。皆用铜铸。毛氏生于千载之后。何以知同律必用竹也。丝有燥湿。竹独无之乎。一寸之竹断而絜之。围为三寸。未几见之。瘦减数分。非燥湿之故乎。匏竹利制者。谓匏竹之声。可大可小。或宫或羽。便于裁制。(利便也)惟议是从也。(云尚议。)伶州鸠本论八音所尚。不言六律所起。岂以利于制律。而谓之利制哉。毛氏欲火太热。凡吾欲所发。即翻弄古文。不少留难。此亦其一也。单穆公极论钟制。继之曰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则十二律之出于钟声。公然明白。犹欲取数寸之管。苦索其蚓窍蝇声。不亦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