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x 页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一)
[序]
[序]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5H 页
 [春秋考徵序]
[春秋考徵序]春秋者。六艺之一。古之所谓左史也。王道行则其一言一动。皆可为经。故书与春秋。列于六经。王迹熄则言皆鄙俚。事皆坏乱。故右史所作。流于词命。左史所记。名为传纪。于是经史分为二门。尊卑邈若九级。其实史未始非经也。然鲁隐以前之史。亡而不传。今所存孔子春秋。则不过存十一于千百。惟其义例。可考而已。余观春秋义例。惟据实直书。而其善恶自见。褒贬予夺。初非执笔者之所能操纵伸缩。乃先儒谈春秋者。每执只字片言。指为夫子之微意。曰诛曰贬曰赏曰褒。阙文落字。穿凿到底。常例故事。傅会唯意。左氏公谷。已犯此病。况于胡文定之盛气哉。有明以来。儒者谓其不然。建旗伐鼓。以明其不必然者。又纷纷然鹊起蜂沸。顾余蒙陋。方应接之弗暇。而况推波而助澜哉。历观先儒之论。惟朱子之说。真确平正。语类所载。千言万语。悉中肯綮。余又何赘。惟是韩宣子之聘鲁。所观者易象春秋。而却云周礼在鲁。(昭二年)则春秋者。周礼之所徵也。欲知周礼者。其不考之于春秋乎。然其事类繁赜。条例浩汗。无以悉举。先执吉凶二礼。别其大纲。以正归趣。略其零碎。以示推通。至于宾军嘉三礼。举一可以反三。苟有同好。庶其补成。今不论也。其草本学圃所受。(嘉庆戊辰冬起草)其再稿李纮父(一作文)所相。(壬申冬编正)书凡十篇。名之曰春秋考徵。
左传云韩宣子(起)来聘。观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昭二年)〇公羊传云(庄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霣星如雨。(何休云不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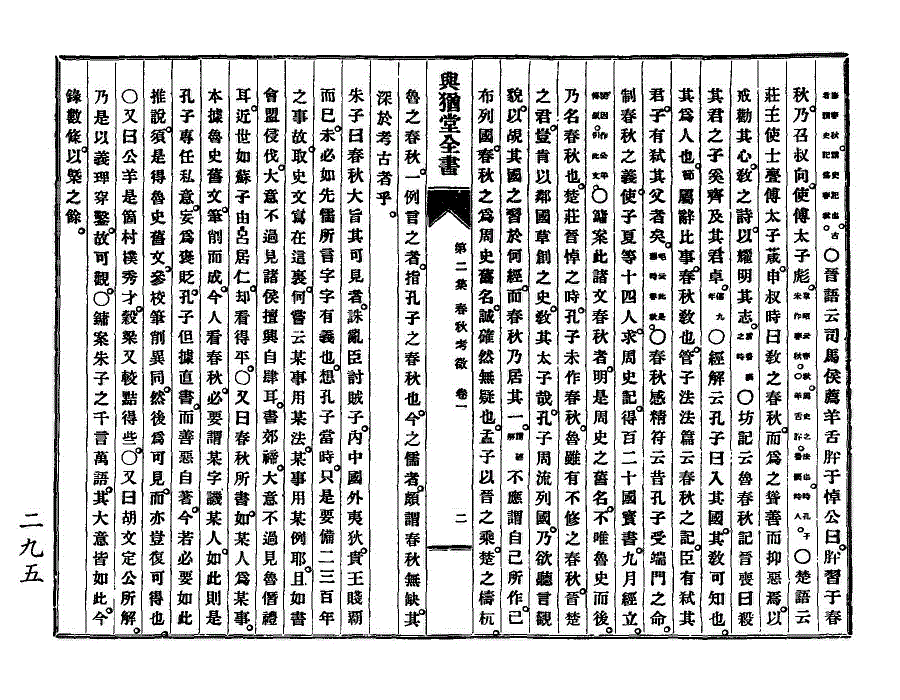 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〇晋语云司马侯荐羊舌肸于悼公曰。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韦昭云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〇羊舌肸。鲁襄时人。)〇楚语云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以耀明其志。(当鲁襄之时)〇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僖九年)〇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节)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管子法法篇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毛云此是旧时春秋。)〇春秋感精符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闵因作公羊传叙。引此文。)〇镛案此诸文春秋者。明是周史之旧名。不唯鲁史而后。乃名春秋也。楚庄晋悼之时。孔子未作春秋。鲁虽有不修之春秋。晋楚之君。岂肯以邻国草创之史。教其太子哉。孔子周流列国。乃欲听言观貌。以觇其国之习于何经。而春秋乃居其一。(谓经解)不应谓自己所作。已布列国。春秋之为周史旧名。诚确然无疑也。孟子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例言之者。指孔子之春秋也。今之儒者。颇谓春秋无缺。其深于考古者乎。
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〇晋语云司马侯荐羊舌肸于悼公曰。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韦昭云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〇羊舌肸。鲁襄时人。)〇楚语云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以耀明其志。(当鲁襄之时)〇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僖九年)〇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节)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管子法法篇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毛云此是旧时春秋。)〇春秋感精符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闵因作公羊传叙。引此文。)〇镛案此诸文春秋者。明是周史之旧名。不唯鲁史而后。乃名春秋也。楚庄晋悼之时。孔子未作春秋。鲁虽有不修之春秋。晋楚之君。岂肯以邻国草创之史。教其太子哉。孔子周流列国。乃欲听言观貌。以觇其国之习于何经。而春秋乃居其一。(谓经解)不应谓自己所作。已布列国。春秋之为周史旧名。诚确然无疑也。孟子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例言之者。指孔子之春秋也。今之儒者。颇谓春秋无缺。其深于考古者乎。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〇又曰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〇又曰公羊是个村朴秀才。谷梁又较黠得些。〇又曰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〇镛案朱子之千言万语。其大意皆如此。今录数条。以槩之馀。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一)
吉礼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6H 页
 郊一(论鲁之郊禘。始于僖公。)
郊一(论鲁之郊禘。始于僖公。)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僖三十一年)
左氏曰非礼也。礼不卜常事。而卜其牲日。(杜云诸侯不得郊天。鲁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礼乐。故郊为鲁常祀。)〇公羊曰卜郊非礼也。(何云天子不卜郊。)鲁郊非礼也。天子祭天。诸侯祭土。(何云周公薨。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〇谷梁曰夏四月。不时也。四卜。非礼也。苑(一作范)云成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〇镛案何休、范宁(一作宁)谓成王命鲁使郊。何据矣。从来说成王赐伯禽天子礼乐者。皆据明堂位一篇。今考明堂位。成王赐周公祀。无赐郊禘。(文见左)曷谓成王命鲁使郊也。周公摄行天子。固天子也。及其薨也。祭以天子。犹之可也。因周公摄行之故。而赐伯禽郊禘。抑何义也。是赐伯禽。非赐周公。伯禽而郊禘。不亦强乎。程子谓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义固正。然有是事而受是罪。罪固甘矣。无是事而处其非。成王伯禽冤矣。今计自鲁隐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一年。其间九十四年也。九十四年者。百年也。百年之间。无岁不郊。而卜则必从。牛则无伤。时则不过。望则不犹。天人相格。鬼神其依。无一灾之可书。忽自僖公三十一年。历宣成襄。下逮定哀。卜则不从。牛则多伤。时则必过。望则必犹。灾孽层生。眚咎叠出。天下有是理乎。何人事之前恪而后慢。鬼神之前宽而后苛欤。是不可知也。余谓鲁之郊禘。僖公之为也。其诗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僖公之禘也。皇皇后帝者。喾之谓也。(详见余诗经讲义)其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僖公之创建也。创建稷庙。以禘喾也。鲁既禘喾。礼应郊稷。鲁之郊禘。不自僖公始乎。礼曰不王不禘。(大传文)余则曰不王不颂。鲁之有颂。自僖公始。鲁之郊禘。非自僖公始乎。始之者僖公。春秋何以不书其始也。春秋有讳恶之义。其始也盖讳之也。然春秋书郊。自僖公始。则郊自僖公始也。其词微。其义彰。夫子不终讳。顾后儒不之觉耳。然则齐桓晋文。何以不讨。曰周之亡也久矣。幽王之亡。而复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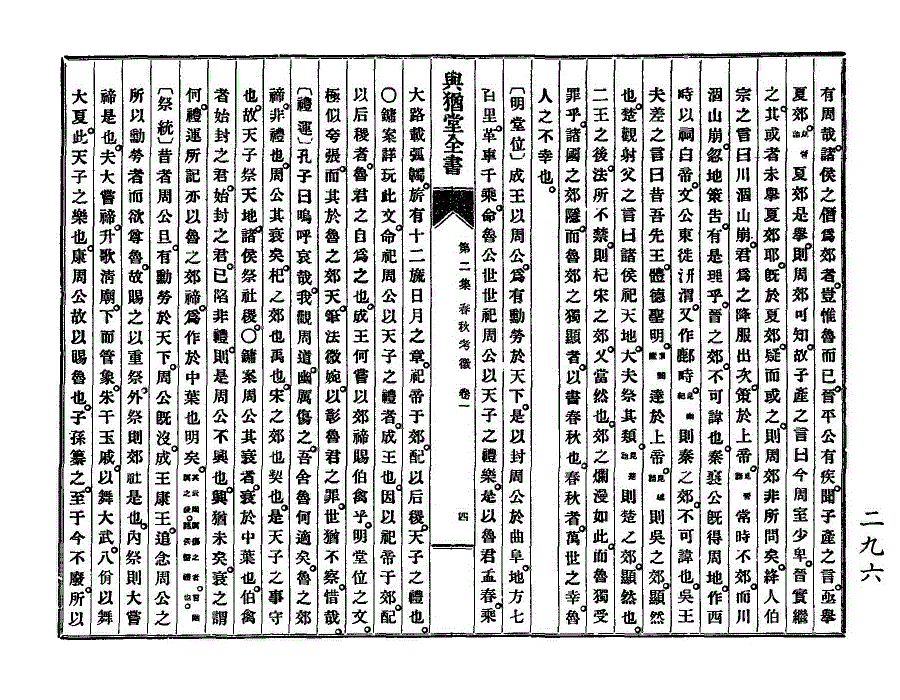 有周哉。诸侯之僭为郊者。岂惟鲁而已。晋平公有疾。闻子产之言。亟举夏郊。(见晋语)夏郊是举。则周郊可知。故子产之言曰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耶。既于夏郊。疑而或之。则周郊非所问矣。绛人伯宗之言曰川涸山崩。君为之降服出次。策于上帝。(见晋语)常时不郊。而川涸山崩。忽地策告。有是理乎。晋之郊。不可讳也。秦襄公既得周地。作西畤以祠白帝。文公东徙汧渭。又作鄜畤。(见秦纪)则秦之郊。不可讳也。吴王夫差之言曰昔吾先王。体德圣明。(谓阖庐)达于上帝。(见越语)则吴之郊。显然也。楚观射父之言曰诸侯祀天地。大夫祭其类。(见楚语)则楚之郊。显然也。二王之后。法所不禁。则杞宋之郊。又当然也。郊之烂漫如此。而鲁独受罪乎。诸国之郊隐。而鲁郊之独显者。以书春秋也。春秋者。万世之幸。鲁人之不幸也。
有周哉。诸侯之僭为郊者。岂惟鲁而已。晋平公有疾。闻子产之言。亟举夏郊。(见晋语)夏郊是举。则周郊可知。故子产之言曰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耶。既于夏郊。疑而或之。则周郊非所问矣。绛人伯宗之言曰川涸山崩。君为之降服出次。策于上帝。(见晋语)常时不郊。而川涸山崩。忽地策告。有是理乎。晋之郊。不可讳也。秦襄公既得周地。作西畤以祠白帝。文公东徙汧渭。又作鄜畤。(见秦纪)则秦之郊。不可讳也。吴王夫差之言曰昔吾先王。体德圣明。(谓阖庐)达于上帝。(见越语)则吴之郊。显然也。楚观射父之言曰诸侯祀天地。大夫祭其类。(见楚语)则楚之郊。显然也。二王之后。法所不禁。则杞宋之郊。又当然也。郊之烂漫如此。而鲁独受罪乎。诸国之郊隐。而鲁郊之独显者。以书春秋也。春秋者。万世之幸。鲁人之不幸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〇镛案详玩此文。命祀周公以天子之礼者。成王也。因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鲁君之自为之也。成王何尝以郊禘赐伯禽乎。明堂位之文。极似夸张。而其于鲁之郊天。笔法微婉。以彰鲁君之罪。世犹不察。惜哉。
〔礼运〕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〇镛案周公其衰者。衰于中叶也。伯禽者始封之君。始封之君。已陷非礼。则是周公不兴也。兴犹未矣。衰之谓何。礼运所记亦以鲁之郊禘。为作于中叶也明矣。(其云幽厉伤之者。言幽厉之后。诸侯僭礼也。)
〔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子孙纂之。至于今不废。所以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7H 页
 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〇镛案道听涂说。莫此记若也。赐鲁重祭者。礼应一赐。不应再赐。乃云成王康王赐以重祭。岂二王皆赐之乎。抑二王同赐之乎。诸侯法当祭社。礼应荐尝。虽无特赐。犹可祭也。此云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尝禘。又何说也。凡祭统所记。多不雅驯。此又不足以破春秋之义也。周襄王之衰弱。而晋文公请隧。不许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僖廿五)况成王康王。何为而赐鲁郊哉。(当时大国多用天子之乐。故孔子在齐闻韶。鲁之大武大夏。又不足言也。)
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〇镛案道听涂说。莫此记若也。赐鲁重祭者。礼应一赐。不应再赐。乃云成王康王赐以重祭。岂二王皆赐之乎。抑二王同赐之乎。诸侯法当祭社。礼应荐尝。虽无特赐。犹可祭也。此云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尝禘。又何说也。凡祭统所记。多不雅驯。此又不足以破春秋之义也。周襄王之衰弱。而晋文公请隧。不许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僖廿五)况成王康王。何为而赐鲁郊哉。(当时大国多用天子之乐。故孔子在齐闻韶。鲁之大武大夏。又不足言也。)〔杨升庵鲁之郊禘辨〕春秋书禘于庄公。见禘之僭。始于闵公也。书四卜郊。见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鲁颂閟宫之三章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以下。则诗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见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春秋。书郊者九。始僖终哀。使隐桓庄闵之世有郊。奚为而不书。鲁颂之颂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鲁颂考之。而知郊禘不出于成王之赐也。(节)隐公尝问羽数于众仲。众仲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八佾之赐。果出成王。则众仲胡不举以对。据此则隐公之世。未有郊可知。庄公观齐社。曹刿谏曰天子事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据此则庄公之世。未有郊可知。皋鼬之盟。苌弘欲先蔡(一作祭)。祝鮀述鲁卫初封之宠命赐物。其说鲁之宠锡。大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纤悉毕举。使有天子礼乐之赐。鮀也正宜藉口。以张大于此时。而反无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赐果出于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讳耶。(周公阅来聘。鲁飨有昌独形盐。而辞不敢受。宁武子聘鲁。鲁飨之。赋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礼。二子之辞。盖恶僭也。鲁之僭未久。故天子之宰。邻国之卿。皆疑怪逊谢。而鲁人并无一语及于成王之赐以自解。)吕氏春秋云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报。盖未允也。此岂非明證大案哉。(明堂位之言。鲁之陋儒欲尊宗国。如亡是公之聘齐也。祭统之说。明堂之枝指也。曰成王康王赐鲁重祭。成王既赐。康王不应复赐。执此以讯。如无情之狱。一鞠而见其肺肝。)〇镛案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7L 页
 纲目前编史角之事。载于鲁惠公之末年。
纲目前编史角之事。载于鲁惠公之末年。郊二(论古之郊期本在建卯之月)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僖三十一年)
传与注疏。已见前。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成十年)
谷梁曰夏四月。不时也。(郊时极于三月。)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襄七年)
左氏引孟献子。详论在下。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襄十一年)
孔云四月四卜。盖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
夏四月辛巳郊。(哀元年)
杜云书过也。〇孔云今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气。故书过也。〇镛案春秋书卜郊者四。书郊者一。皆在夏四月。夏四月者。建卯之月。夏正之二月也。(春分之月)卯月为郊之定期。故卜郊必于卯月。其卜从而行祭如期者。常事也。不书其不从。而过期不祭者书之。经例昭然。哀元年之书之者。以鼷鼠食角。危不得祭。故幸而书之也。左氏公羊以寅月为郊期。谷梁以子月为郊期。其义皆非也。若鲁人无礼。好行不时之祭。则丑月寅月辰月巳月。必其卜错杂而无恒。胡乃春秋所书卜郊之事。必皆卯月。无他月乎。卯月之为郊之本期明矣。且所云四卜郊五卜郊者。决非是月之郊。而是月卜之也。曲礼云凡卜日之法。吉事先近日。(旬之内曰近日)而郊祭本用辛日。若卜近而吉。又朔是辛。则必将行事于朔日矣。凡祭散齐七日。致齐三日。又前期十日矣。是月之郊。而是月卜之。奚可及哉。然则其所谓四卜郊五卜郊者。必皆前一月而卜之也。(孔疏云一卜在四月者。谓卜下旬则容可然也。)卯月行事则寅月卜之也明矣。寅月卜之而乃于卯月书之曰四卜郊不从乃不郊。曰五卜郊不从乃不郊。则卯月之为郊之定期。尤昭昭然矣。本非礼月则书不郊何义也。诸凡不书之年。皆卯月行事如其期也。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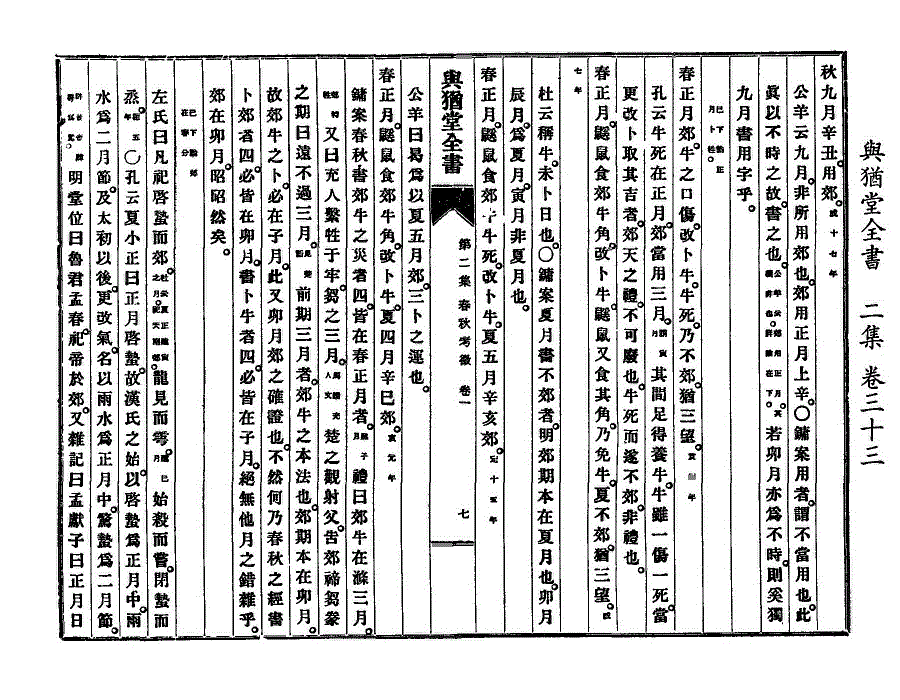 秋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年)
秋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年)公羊云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〇镛案用者。谓不当用也。此真以不时之故。书之也。(公羊云郊用正月。其义非也。详论在下。)若卯月亦为不时。则奚独九月书用字乎。
(已下论正月卜牲。)
春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宣三年)
孔云牛死在正月。郊当用三月。(谓寅月)其间足得养牛。牛虽一伤一死。当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礼。不可废也。牛死而遂不郊。非礼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不郊。犹三望。(成七年)
杜云称牛。未卜日也。〇镛案夏月书不郊者。明郊期本在夏月也。卯月辰月。为夏月。寅月非夏月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定十五年)
公羊曰曷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运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哀元年)
镛案春秋书郊牛之灾者四。皆在春正月者。(建子月)礼曰郊牛在涤三月。(郊特牲)又曰充人系牲于牢。刍之三月。(周礼充人文)楚之观射父。告郊禘刍豢之期曰远不过三月。(见楚语)前期三月者。郊牛之本法也。郊期本在卯月。故郊牛之卜。必在子月。此又卯月郊之确證也。不然何乃春秋之经书卜郊者四。必皆在卯月。书卜牛者四。必皆在子月。绝无他月之错杂乎。郊在卯月。昭昭然矣。
(已下论郊在春分)
左氏曰凡祀启蛰而郊。(杜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龙见而雩。(建巳月)始杀而尝。闭蛰而烝。(桓五年)〇孔云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故汉氏之始。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辟景帝讳启为惊。)明堂位曰鲁君孟春。祀帝于郊。又杂记曰孟献子曰正月日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8L 页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如彼记文。则鲁郊以周之孟春。而传言启蛰而郊者。礼记后人所录。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礼。襄七年传。孟献子曰启蛰而郊。礼记左传俱称献子。而记言日至。传言启蛰。一人两说。必有谬者。是知献子本无此言。此俱云。左传非也。〇镛案启蛰者。春分之候。非寅月之气也。夏小正其首句曰正月启蛰。一月六候。则立春之首五日启蛰也。谁见立春之初。蛰虫启户乎。汉初以启蛰为中气。则退半月也。武帝时以为二月之节。则又退半月也。犹非启户之时。则改之曰惊蛰。(不但辟讳而改之。)惊者警也。日气渐舒。则蛰魂醒寤也。(如死之复生)启者开也。日晷正中。则蛰户始辟也。(乃启户而出)今据目之所睹。蛰燕蛰蛇之等。皆于春分之后。始见其形。几见正月之中。二月之初。蛰虫发动乎。吕氏月令。蛰虫坯户。实在八月中候之后。坯户在秋分之后。则启户在春分之后。理所宜然。揆诸天道而合。考诸物性而叶。夏小正者。戴氏私传之书。不足凭也。然则自古相传曰启蛰而郊者。是上古之遗文。孟献子、左丘明。非创为之言也。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如彼记文。则鲁郊以周之孟春。而传言启蛰而郊者。礼记后人所录。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礼。襄七年传。孟献子曰启蛰而郊。礼记左传俱称献子。而记言日至。传言启蛰。一人两说。必有谬者。是知献子本无此言。此俱云。左传非也。〇镛案启蛰者。春分之候。非寅月之气也。夏小正其首句曰正月启蛰。一月六候。则立春之首五日启蛰也。谁见立春之初。蛰虫启户乎。汉初以启蛰为中气。则退半月也。武帝时以为二月之节。则又退半月也。犹非启户之时。则改之曰惊蛰。(不但辟讳而改之。)惊者警也。日气渐舒。则蛰魂醒寤也。(如死之复生)启者开也。日晷正中。则蛰户始辟也。(乃启户而出)今据目之所睹。蛰燕蛰蛇之等。皆于春分之后。始见其形。几见正月之中。二月之初。蛰虫发动乎。吕氏月令。蛰虫坯户。实在八月中候之后。坯户在秋分之后。则启户在春分之后。理所宜然。揆诸天道而合。考诸物性而叶。夏小正者。戴氏私传之书。不足凭也。然则自古相传曰启蛰而郊者。是上古之遗文。孟献子、左丘明。非创为之言也。左氏曰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襄七年)〇镛案此即上夏四月三卜郊之传也。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此二句八字。必系三古之遗文。非后世之人所能言也。大义玄远。未易言也。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万物出乎震。震者二月春分之位。东方正中之卦也。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亦以震一阳为乾元之始。而首出之圣。应乎震也。(春分为震方之正中。)郊期之必于春分之际。玄义在此。故知二句八字。为三古之遗文也。孟献子乃以郊天大祭。专主祈农之意。此谬义也。周人之郊。适以后稷配食。故献子之言如此耳。有虞氏郊尧。(祭法云郊喾)夏后氏郊鲧。殷人郊冥。此三人者。本非农官。岂亦祈谷而郊之乎。春分之郊。非祈农也。
(已下论子月寅月非郊期。)
谷梁氏曰夏四月。不时也。(郊时极于三月)五卜。强也。(成十年)〇又曰(哀元年)郊自正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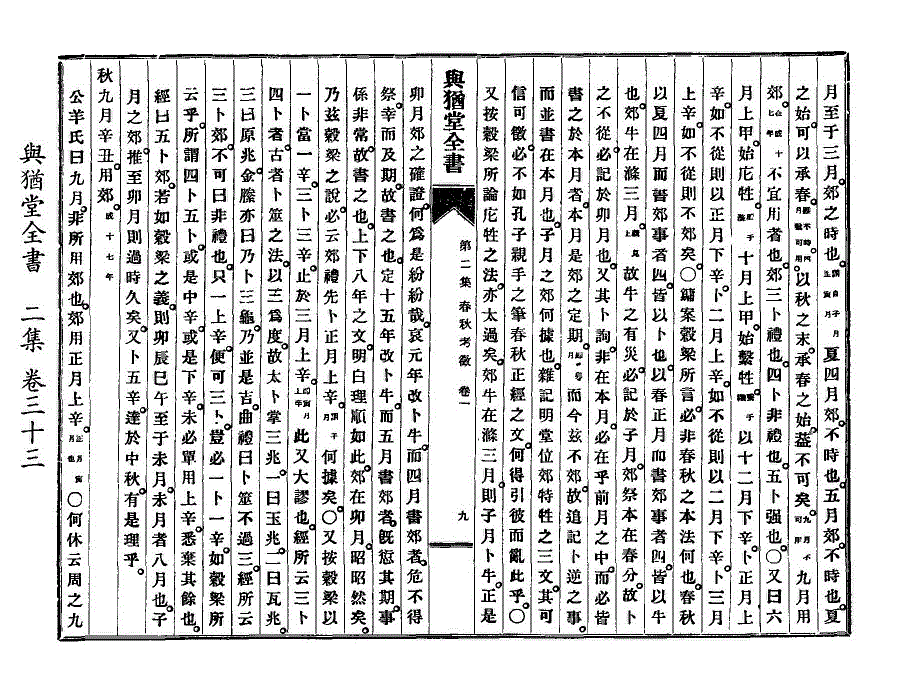 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谓自子月至寅月)夏四月郊。不时也。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虽不时。四月犹可用。)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不可用)九月用郊。(在成十七年)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强也。〇又曰六月上甲。始庀牲。(置于涤)十月上甲。始系牲。(系于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〇镛案谷梁所言。必非春秋之本法何也。春秋以夏四月而书郊事者四。皆以卜也。以春正月而书郊事者四。皆以牛也。郊牛在涤三月。(义见上)故牛之有灾。必记于子月。郊祭本在春分。故卜之不从。必记于卯月也。又其卜询。非在本月。必在乎前月之中。而必皆书之于本月者。本月是郊之定期。(即卯月)而今玆不郊。故追记卜逆之事。而并书在本月也。子月之郊何据也。杂记明堂位郊特牲之三文。其可信可徵。必不如孔子亲手之笔春秋正经之文。何得引彼而乱此乎。〇又按谷梁所论庀牲之法。亦太过矣。郊牛在涤三月。则子月卜牛。正是卯月郊之确證。何为是纷纷哉。哀元年改卜牛。而四月书郊者。危不得祭。幸而及期。故书之也。定十五年改卜牛。而五月书郊者。既愆其期。事系非常。故书之也。上下八年之文。明白理顺如此。郊在卯月。昭昭然矣。乃玆谷梁之说。必云郊礼先卜正月上辛。(谓子月)何据矣。〇又按谷梁以一卜当一辛。三卜三辛。止于三月上辛。(即寅月上辛)此又大谬也。经所云三卜四卜者。古者卜筮之法。以三为度。故太卜掌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金縢亦曰乃卜三龟。乃并是吉。曲礼曰卜筮不过三。经所云三卜郊。不可曰非礼也。只一上辛。便可三卜。岂必一卜一辛。如谷梁所云乎。所谓四卜五卜。或是中辛。或是下辛。未必单用上辛。悉弃其馀也。经曰五卜郊。若如谷梁之义。则卯辰巳午至于未月。未月者八月也。子月之郊。推至(一作之)卯月则过时久矣。又卜五辛。达于中秋。有是理乎。
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谓自子月至寅月)夏四月郊。不时也。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虽不时。四月犹可用。)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不可用)九月用郊。(在成十七年)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强也。〇又曰六月上甲。始庀牲。(置于涤)十月上甲。始系牲。(系于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〇镛案谷梁所言。必非春秋之本法何也。春秋以夏四月而书郊事者四。皆以卜也。以春正月而书郊事者四。皆以牛也。郊牛在涤三月。(义见上)故牛之有灾。必记于子月。郊祭本在春分。故卜之不从。必记于卯月也。又其卜询。非在本月。必在乎前月之中。而必皆书之于本月者。本月是郊之定期。(即卯月)而今玆不郊。故追记卜逆之事。而并书在本月也。子月之郊何据也。杂记明堂位郊特牲之三文。其可信可徵。必不如孔子亲手之笔春秋正经之文。何得引彼而乱此乎。〇又按谷梁所论庀牲之法。亦太过矣。郊牛在涤三月。则子月卜牛。正是卯月郊之确證。何为是纷纷哉。哀元年改卜牛。而四月书郊者。危不得祭。幸而及期。故书之也。定十五年改卜牛。而五月书郊者。既愆其期。事系非常。故书之也。上下八年之文。明白理顺如此。郊在卯月。昭昭然矣。乃玆谷梁之说。必云郊礼先卜正月上辛。(谓子月)何据矣。〇又按谷梁以一卜当一辛。三卜三辛。止于三月上辛。(即寅月上辛)此又大谬也。经所云三卜四卜者。古者卜筮之法。以三为度。故太卜掌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金縢亦曰乃卜三龟。乃并是吉。曲礼曰卜筮不过三。经所云三卜郊。不可曰非礼也。只一上辛。便可三卜。岂必一卜一辛。如谷梁所云乎。所谓四卜五卜。或是中辛。或是下辛。未必单用上辛。悉弃其馀也。经曰五卜郊。若如谷梁之义。则卯辰巳午至于未月。未月者八月也。子月之郊。推至(一作之)卯月则过时久矣。又卜五辛。达于中秋。有是理乎。秋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年)
公羊氏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正月。寅月也。)〇何休云周之九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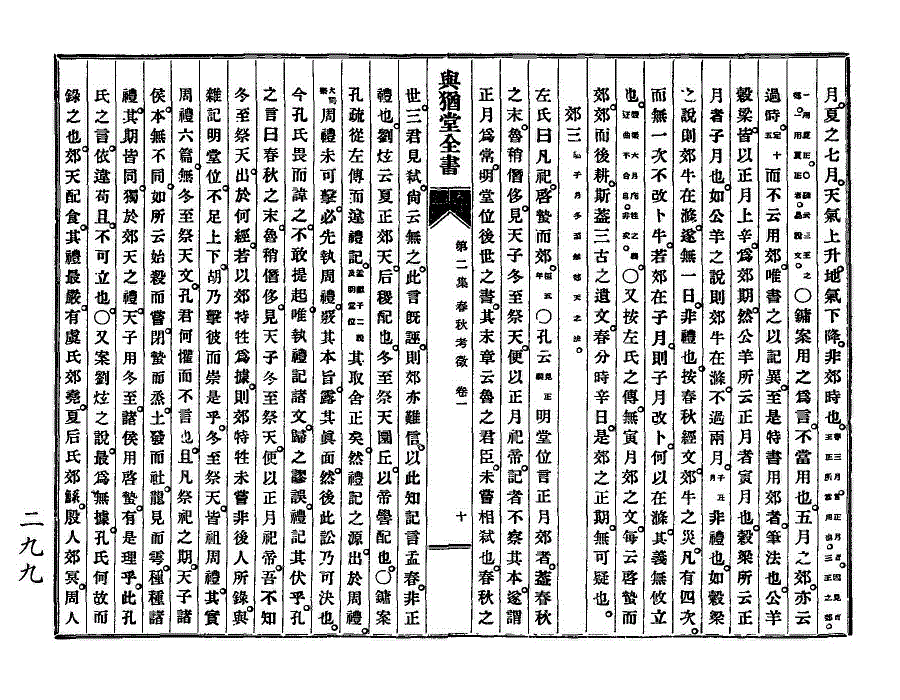 月。夏之七月。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非郊时也。(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见百王正所当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〇疏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说文。)〇镛案用之为言。不当用也。五月之郊。亦云过时。(定十五)而不云用郊。唯书之以记异。至是特书用郊者。笔法也。公羊谷梁。皆以正月上辛为郊期。然公羊所云正月者寅月也。谷梁所云正月者子月也。如公羊之说则郊牛在涤。不过两月。(子丑月)非礼也。如谷梁之说则郊牛在涤。遂无一日。非礼也。按春秋经文。郊牛之灾。凡有四次。而无一次不改卜牛。若郊在子月。则子月改卜。何以在涤。其义无攸立也。(谷梁六月庀牲之义。迂曲不合理。非矣。)〇又按左氏之传。无寅月郊之文。每云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斯盖三古之遗文。春分时辛日。是郊之正期。无可疑也。
月。夏之七月。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非郊时也。(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见百王正所当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〇疏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说文。)〇镛案用之为言。不当用也。五月之郊。亦云过时。(定十五)而不云用郊。唯书之以记异。至是特书用郊者。笔法也。公羊谷梁。皆以正月上辛为郊期。然公羊所云正月者寅月也。谷梁所云正月者子月也。如公羊之说则郊牛在涤。不过两月。(子丑月)非礼也。如谷梁之说则郊牛在涤。遂无一日。非礼也。按春秋经文。郊牛之灾。凡有四次。而无一次不改卜牛。若郊在子月。则子月改卜。何以在涤。其义无攸立也。(谷梁六月庀牲之义。迂曲不合理。非矣。)〇又按左氏之传。无寅月郊之文。每云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斯盖三古之遗文。春分时辛日。是郊之正期。无可疑也。郊三(论子月冬至无郊天之法。)
左氏曰凡祀。启蛰而郊。(桓五年)〇孔云(见正义)明堂位言正月郊者。盖春秋之末。鲁稍僭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记者不察其本。遂谓正月为常。明堂位后世之书。其末章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也。春秋之世。三君见弑。尚云无之。此言既诬。则郊亦难信。以此知记言孟春。非正礼也。刘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喾配也。〇镛案孔疏从左传而违礼记。(孟献子二说及明堂位)其取舍正矣。然礼记之源。出于周礼。(大司乐)周礼未可击。必先执周礼。覈其本旨。露其真面。然后此讼乃可决也。今孔氏畏而讳之。不敢提起。唯执礼记诸文。归之谬误。礼记其伏乎。孔之言曰春秋之末。鲁稍僭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吾不知冬至祭天。出于何经。若以郊特牲为据。则郊特牲未尝非后人所录。与杂记明堂位。不足上下。胡乃击彼而崇是乎。冬至祭天。皆祖周礼。其实周礼六篇。无冬至祭天文。孔君何惧而不言也。且凡祭祀之期。天子诸侯。本无不同。如所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烝。土发而社。龙见而雩。种种诸礼。其期皆同。独于郊天之礼。天子用冬至。诸侯用启蛰。有是理乎。此孔氏之言。依违苟且。不可立也。〇又案刘炫之说。最为无据。孔氏何故而录之也。郊天配食。其礼最严。有虞氏郊尧。夏后氏郊鲧。殷人郊冥。周人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0H 页
 郊稷。(鲁展禽之语。)一代所郊。止有一人。夏正郊稷。冬至郊喾。天下有是礼乎。虽两经双隆。犹当违一而从一。况冬至祭天。其在周礼。本无影响。今必欲两立而双尊之。抑何故也。冬至祭天之说。皆以大司乐圜丘奏乐之文为祖。其实圜丘奏乐。非祭上帝也。今疏理如左。
郊稷。(鲁展禽之语。)一代所郊。止有一人。夏正郊稷。冬至郊喾。天下有是礼乎。虽两经双隆。犹当违一而从一。况冬至祭天。其在周礼。本无影响。今必欲两立而双尊之。抑何故也。冬至祭天之说。皆以大司乐圜丘奏乐之文为祖。其实圜丘奏乐。非祭上帝也。今疏理如左。〔周礼〕大司乐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谐万民。以作动物。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节)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〇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节)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节)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节)九德之歌。九㲈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上文云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裸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〇镛案详玩此文。祭与奏乐。判为二事。祭天神则所用惟黄钟大吕。其奏乐则圜钟黄钟大蔟姑洗。备用四音。合为一事则不可通也。祭地示则所用惟大蔟应钟。其奏乐则函钟大蔟姑洗南吕。备用四音。合为一事则不可通也。祭天祭地。虽有定月。本无定日。故春秋传云启蛰而郊。(见左传)土发而社。(春分也。见鲁语。)其奏乐则用冬至夏至。合为一事则不可通也。圜丘非郊。(古经无以圜丘为郊者。)方丘非社。(方丘在泽中。社坛在国城之内。)合为一事则不可通也。祭所主者一神。(或主上帝。或主日月等。)一示。(或主后土。或主山川等。)奏乐则曰天神皆降。地示皆出。皆之为言。明非一也。(宗庙不言皆。其文可知。)所主非一。明非祭也。合为一事则不可通也。故春官笃(一作篇)末。明以二至奏乐。为禬除之礼。(文见下)与郊社禘尝之正祭。判为二事。了不相混。乃秦末俗儒。误读周礼。遂作郊特牲一篇。谬谓郊祭在于冬至。(文见下)于是伪造孟献子一语。插之杂记。(文见下)一人两说。显相矛盾。又为鲁君孟春郊天之说。以饰明堂位一篇。及至王莽之时。乃以冬至祀南郊。夏至祀北郊。而郑玄酷信谶纬。其注三礼。俨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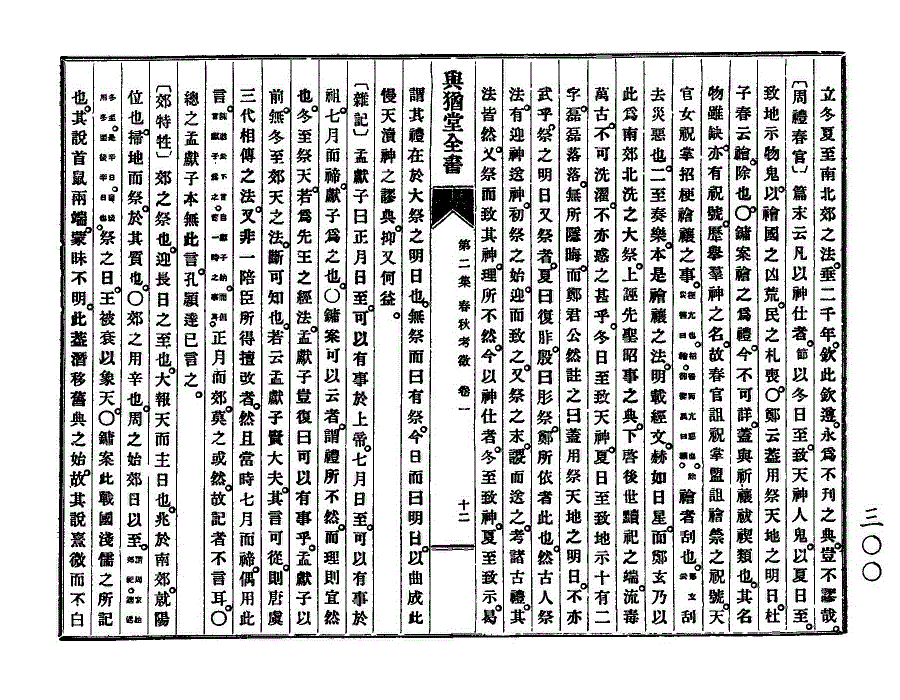 立冬夏至南北郊之法。垂二千年。钦此钦遵。永为不刊之典。岂不谬哉。
立冬夏至南北郊之法。垂二千年。钦此钦遵。永为不刊之典。岂不谬哉。〔周礼春官〕篇末云凡以神仕者。(节)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禬国之凶荒。民之札丧。〇郑云盖用祭天地之明日。杜子春云禬。除也。〇镛案禬之为礼。今不可详。盖与祈禳祓禊类也。其名物虽缺。亦有祝号。历举群神之名。故春官诅祝掌盟诅禬禜之祝号。天官女祝掌招梗禬禳之事。(梗。亢也。招善而亢恶也。除灾害曰禬。却变异曰禳。)禬者刮也。(郑玄云。)刮去灾恶也。二至奏乐。本是禬禳之法。明载经文。赫如日星。而郑玄乃以此为南郊北洗(一作郊)之大祭。上诬先圣昭事之典。下启后世黩祀之端。流毒万古。不可洗濯。不亦惑之甚乎。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致地示十有二字。磊磊落落。无所隐晦。而郑君公然注之曰盖用祭天地之明日。不亦武乎。祭之明日又祭者。夏曰复胙。殷曰肜祭。郑所依者此也。然古人祭法。有迎神送神。初祭之始。迎而致之。又祭之末。谡而送之。考诸古礼。其法皆然。又祭而致其神。理所不然。今以神仕者。冬至致神。夏至致示。曷谓其礼在于大祭之明日也。无祭而曰有祭。今日而曰明日。以曲成此慢天渎神之谬典。抑又何益。
〔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〇镛案可以云者。谓礼所不然。而理则宜然也。冬至祭天。若为先王之经法。孟献子岂复曰可以有事乎。孟献子以前。无冬至郊天之法。断可知也。若云孟献子贤大夫。其言可从。则唐虞三代相传之法。又非一陪臣所得擅改者。然且当时七月而禘。偶用此言。(陈浩云不言自献子始。而但言献子为之。盖一时之事耳。)正月而郊。莫之或然。故记者不言耳。总之孟献子本无此言。孔颖达已言之。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谓周家始郊祀。适遇冬至。是辛日。自后用冬至后辛日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〇镛案此战国浅儒之所记也。其说首鼠两端。蒙昧不明。此盖潜移旧典之始。故其说熹微而不白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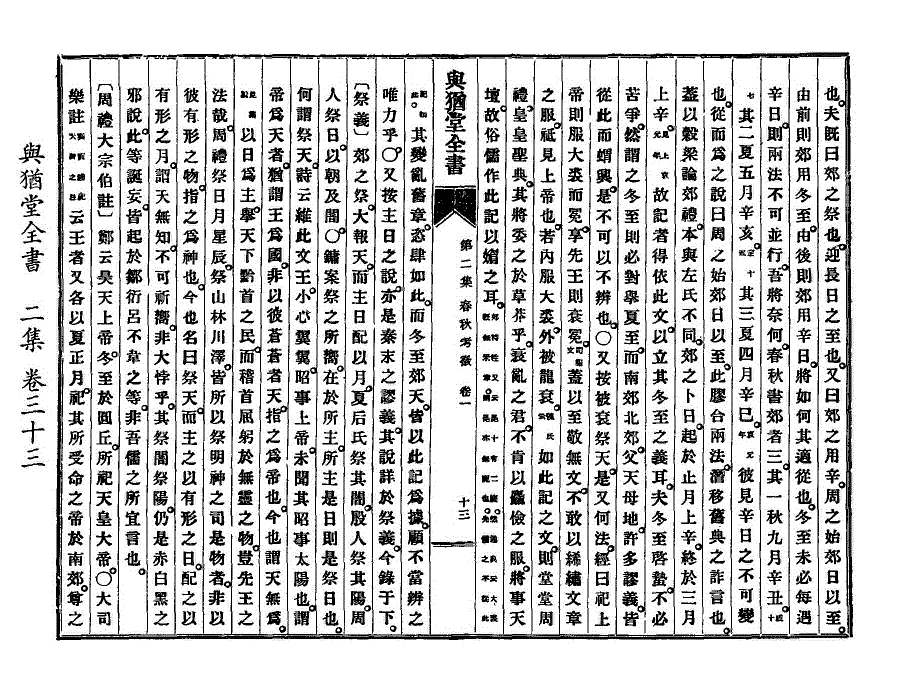 也。夫既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由前则郊用冬至。由后则郊用辛日。将如何其适从也。冬至未必每遇辛日。则两法不可并行。吾将奈何。春秋书郊者三。其一秋九月辛丑。(成十七)其二夏五月辛亥。(定十五)其三夏四月辛巳。(哀元年)彼见辛日之不可变也。从而为之说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胶合两法。潜移旧典之诈言也。盖以谷梁论郊礼。本与左氏不同。郊之卜日。起于止(一作正)月上辛。终于三月上辛。(见上哀元年)故记者得依此文。以立其冬至之义耳。夫冬至启蛰。不必苦争。然谓之冬至则必对举夏至。而南郊北郊。父天母地。许多谬义。皆从此而猬兴。是不可以不辨也。〇又按被衮祭天。是又何法。经曰祀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司服文)盖以至敬无文。不敢以絺绣文章之服。祗见上帝也。若内服大裘。外被龙衮。(陈氏云)如此记之文。则堂堂周礼。皇皇圣典。其将委之于草莽乎。衰乱之君。不肯以粗俭之服。将事天坛。故俗儒作此记以媚之耳。(郊特牲又云冕十有二旒。然通典云大裘既无采章。则冕亦无旒也。先儒之不从此记如此。)其变乱旧章。恣肆如此。而冬至郊天。皆以此记为据。顾不当辨之唯力乎。〇又按主日之说。亦是秦末之谬义。其说详于祭义。今录于下。
也。夫既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由前则郊用冬至。由后则郊用辛日。将如何其适从也。冬至未必每遇辛日。则两法不可并行。吾将奈何。春秋书郊者三。其一秋九月辛丑。(成十七)其二夏五月辛亥。(定十五)其三夏四月辛巳。(哀元年)彼见辛日之不可变也。从而为之说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胶合两法。潜移旧典之诈言也。盖以谷梁论郊礼。本与左氏不同。郊之卜日。起于止(一作正)月上辛。终于三月上辛。(见上哀元年)故记者得依此文。以立其冬至之义耳。夫冬至启蛰。不必苦争。然谓之冬至则必对举夏至。而南郊北郊。父天母地。许多谬义。皆从此而猬兴。是不可以不辨也。〇又按被衮祭天。是又何法。经曰祀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司服文)盖以至敬无文。不敢以絺绣文章之服。祗见上帝也。若内服大裘。外被龙衮。(陈氏云)如此记之文。则堂堂周礼。皇皇圣典。其将委之于草莽乎。衰乱之君。不肯以粗俭之服。将事天坛。故俗儒作此记以媚之耳。(郊特牲又云冕十有二旒。然通典云大裘既无采章。则冕亦无旒也。先儒之不从此记如此。)其变乱旧章。恣肆如此。而冬至郊天。皆以此记为据。顾不当辨之唯力乎。〇又按主日之说。亦是秦末之谬义。其说详于祭义。今录于下。〔祭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〇镛案祭之所向。在于所主。所主是日则是祭日也。何谓祭天。诗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未闻其昭事太阳也。谓帝为天者。犹谓王为国。非以彼苍苍者天。指之为帝也。今也谓天无为。(见集说)以日为主。举天下黔首之民。而稽首屈躬于无灵之物。岂先王之法哉。周礼祭日月星辰。祭山林川泽。皆所以祭明神之司是物者。非以彼有形之物。指之为神也。今也名曰祭天。而主之以有形之日。配之以有形之月。谓天无知。不可祈向。非大悖乎。其祭闇祭阳。仍是赤白黑之邪说。此等诞妄。皆起于邹衍吕不韦之等。非吾儒之所宜言也。
〔周礼大宗伯注〕郑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圆丘。所祀天皇大帝。〇大司乐注。(奏黄钟祀天神之注)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尊之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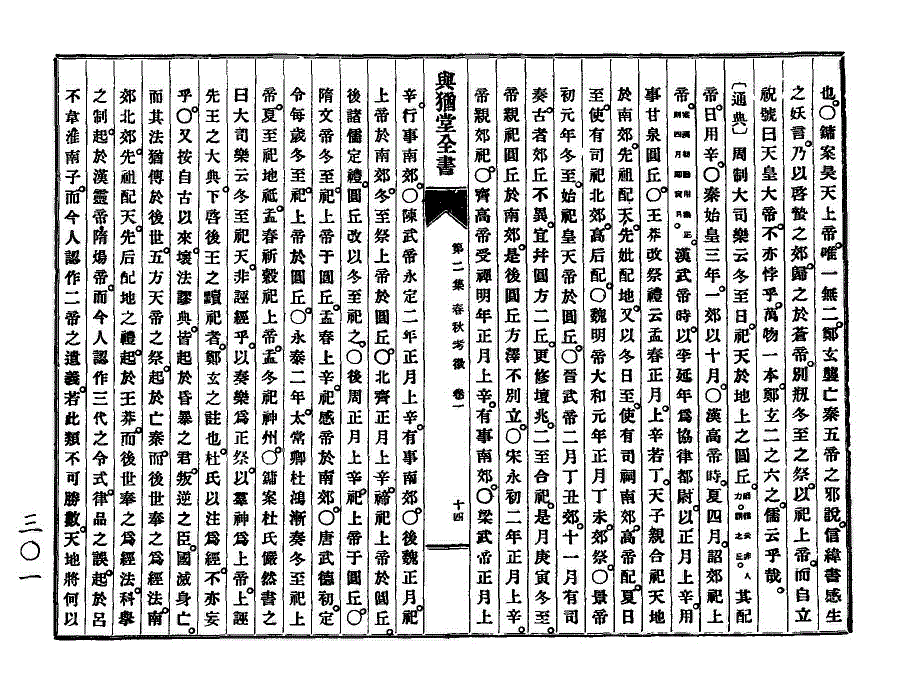 也。〇镛案昊天上帝。唯一无二。郑玄袭亡秦五帝之邪说。信纬书感生之妖言。乃以启蛰之郊。归之于苍帝。别创冬至之祭。以祀上帝。而自立祝号曰天皇大帝。不亦悖乎。万物一本。郑玄二之六之。儒云乎哉。
也。〇镛案昊天上帝。唯一无二。郑玄袭亡秦五帝之邪说。信纬书感生之妖言。乃以启蛰之郊。归之于苍帝。别创冬至之祭。以祀上帝。而自立祝号曰天皇大帝。不亦悖乎。万物一本。郑玄二之六之。儒云乎哉。〔通典〕周制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圆丘。(尔雅云非人力。谓之丘。)其配帝。日用辛。〇秦始皇三年。一郊以十月。〇汉高帝时。夏四月。诏郊祀上帝。(案汉初犹用秦正。则四月即寅月。)汉武帝时。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〇王莽改祭礼云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又以冬日至。使有司祠南郊。高帝配。夏日至。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〇魏明帝大(一作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〇景帝初元年冬至。始祀皇天帝于圆丘。〇晋武帝二月丁丑郊。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异。宜并圆方二丘。更修坛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〇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亲郊祀。〇齐高帝受禫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〇梁武帝正月上辛。行事南郊。〇陈武帝永定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〇后魏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冬至祭上帝于圆丘。〇北齐正月上辛。禘祀上帝于圆丘。后诸儒定礼。圆丘改以冬至祀之。〇后周正月上辛。祀上帝于圆丘。〇隋文帝冬至。祀上帝于圆丘。孟春上辛。祀感帝于南郊。〇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上帝于圆丘。〇永泰二年。太常卿杜鸿渐奏冬至祀上帝。夏至祀地祗。孟春祈谷祀上帝。孟冬祀神州。〇镛案杜氏俨然书之曰大司乐云冬至祀天。非诬经乎。以奏乐为正祭。以群神为上帝。上诬先王之大典。下启后王之黩祀者。郑玄之注也。杜氏以注为经。不亦妄乎。〇又按自古以来。坏法谬典。皆起于昏暴之君。叛逆之臣。国灭身亡。而其法犹传于后世。五方天帝之祭。起于亡秦。而后世奉之为经法。南郊北郊。先祖配天。先后配地之礼。起于王莽。而后世奉之为经法。科举之制。起于汉灵帝、隋炀帝。而今人认作三代之令式。律品(一作吕)之误。起于吕不韦淮南子。而今人认作二帝之遗义。若此类不可胜数。天地将何以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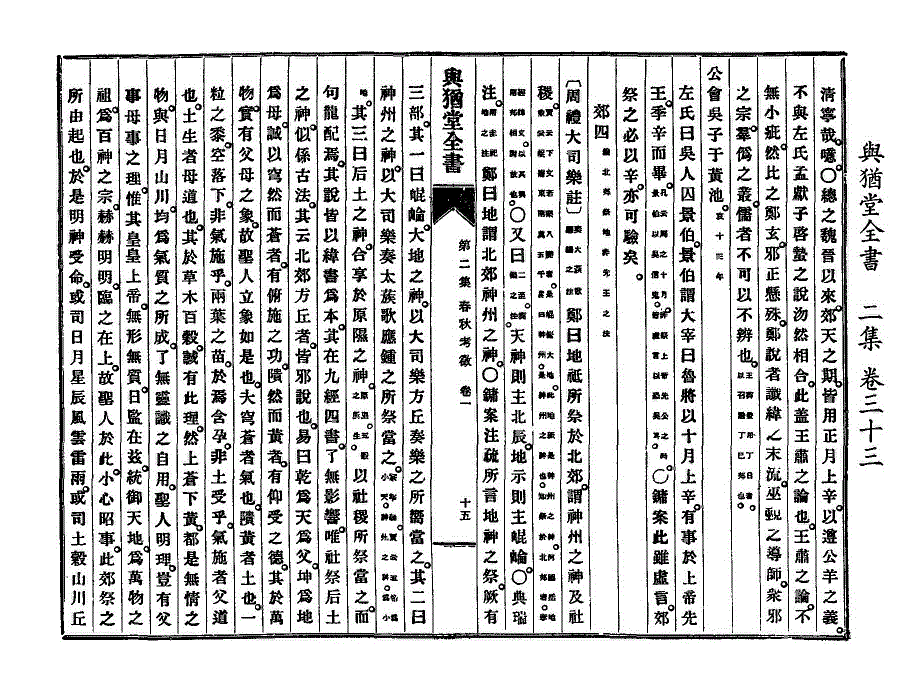 清宁哉。噫。〇总之魏晋以来。郊天之期。皆用正月上辛。以遵公羊之义。不与左氏孟献子启蛰之说沕然相合。此盖王肃之论也。王肃之论。不无小疵。然比之郑玄。邪正悬殊。郑说者谶纬之末流。巫觋之导师。众邪之宗。群伪之丛。儒者不可以不辨也。(王莽兼用丁日者。以召诰丁巳郊也。)
清宁哉。噫。〇总之魏晋以来。郊天之期。皆用正月上辛。以遵公羊之义。不与左氏孟献子启蛰之说沕然相合。此盖王肃之论也。王肃之论。不无小疵。然比之郑玄。邪正悬殊。郑说者谶纬之末流。巫觋之导师。众邪之宗。群伪之丛。儒者不可以不辨也。(王莽兼用丁日者。以召诰丁巳郊也。)公会吴子于黄池。(哀十三年)
左氏曰吴人囚景伯。景伯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孔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时。景伯以吴信鬼。皆虚言以恐吴耳。)〇镛案此虽虚言。郊祭之必以辛。亦可验矣。
郊四(论北郊祭地非先王之法)
〔周礼大司乐注〕(奏大蔟歌应钟之注)郑曰地祗所祭于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贾云下文若乐八变者。是昆崙大地。此地祗是神州之神。河图括地象云昆崙东南万五千里曰神州。是神州之神也。知祭于北郊者。孝经纬文。以其与南郊相对故也。)〇又曰(二至。奏乐之注。)天神则主北辰。地示则主昆崙。〇典瑞注(两圭祀地之注)郑曰地谓北郊神州之神。〇镛案注疏所言地神之祭。厥有三部。其一曰昆崙。大地之神。以大司乐方丘奏乐之所向当之。其二曰神州之神。以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钟之所祭当之。(冢宰疏。贾云五帝为小天。神州之神。为小地。)其三曰后土之神。合享于原隰之神。(原湿。五谷之所生。)以社稷所祭当之。而句龙配焉。其说皆以纬书为本。其在九经四书。了无影响。唯社祭后土之神。似系古法。其云北郊方丘者。皆邪说也。易曰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诚以穹然而苍者。有俯施之功。隤然而黄者。有仰受之德。其于万物。实有父母之象。故圣人立象如是也。夫穹苍者气也。隤黄者土也。一粒之黍。从空落下。非气施乎。两叶之苗。于焉含孕。非土受乎。气施者父道也。土生者母道也。其于草木百谷。诚有此理。然上苍下黄。都是无情之物。与日月山川。均为气质之所成。了无灵识之自用。圣人明理。岂有父事母事之理。惟其皇皇上帝。无形无质。日监在兹。统御天地。为万物之祖。为百神之宗。赫赫明明。临之在上。故圣人于此。小心昭事。此郊祭之所由起也。于是明神受命。或司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或司土谷山川丘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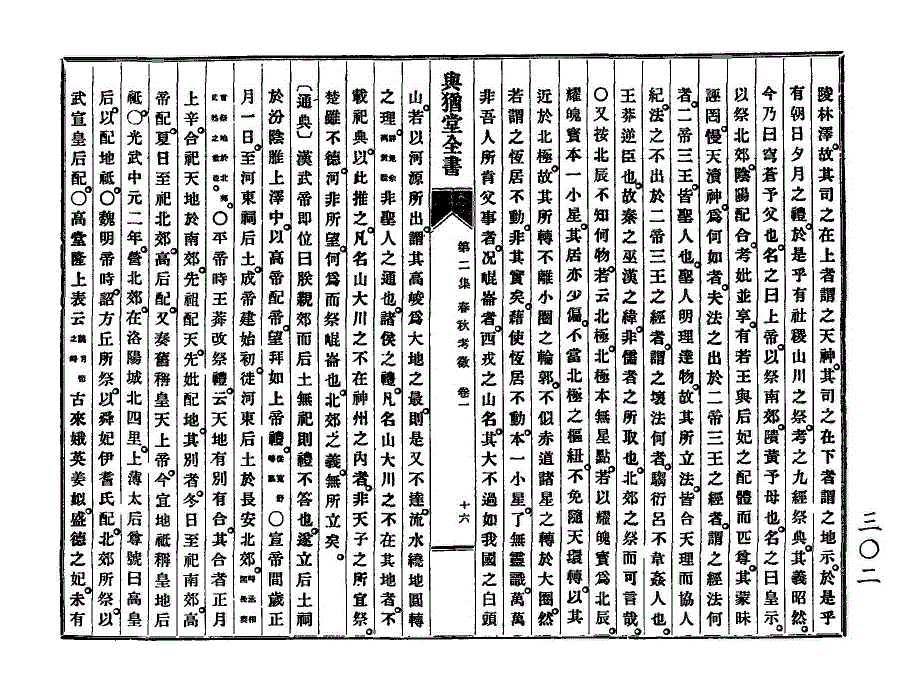 陵林泽。故其司之在上者谓之天神。其司之在下者谓之地示。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之礼。于是乎有社稷山川之祭。考之九经祭典。其义昭然。今乃曰穹苍予父也。名之曰上帝。以祭南郊。隤黄予母也。名之曰皇示。以祭北郊。阴阳配合。考妣并享。有若王与后妃之配体而匹尊。其蒙昧诬罔。慢天渎神。为何如者。夫法之出于二帝三王之经者。谓之经法何者。二帝三王。皆圣人也。圣人明理达物。故其所立法。皆合天理而协人纪。法之不出于二帝三王之经者。谓之坏法何者。驺衍吕不韦奸人也。王莽逆臣也。故秦之巫汉之纬。非儒者之所取也。北郊之祭而可言哉。〇又按北辰不知何物。若云北极。北极本无星点。若以耀魄宝为北辰。耀魄宝本一小星。其居亦少(一作小)偏。不当北极之枢纽。不免随天环转。以其近于北极。故其所转不离小圈之轮郭。不似赤道诸星之转于大圈。然若谓之恒居不动。非其实矣。藉使恒居不动。本一小星。了无灵识。万万非吾人所肯父事者。况昆崙者。西戎之山名。其大不过如我国之白头山。若以河源所出。谓其高峻为大地之最。则是又不达。流水绕地圆转之理。(详见余禹贡说)非圣人之通也。诸侯之礼。凡名山大川之不在其地者。不载祀典。以此推之。凡名山大川之不在神州之内者。非天子之所宜祭。楚虽不德。河非所望。何为而祭昆崙也。北郊之义。无所立矣。
陵林泽。故其司之在上者谓之天神。其司之在下者谓之地示。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之礼。于是乎有社稷山川之祭。考之九经祭典。其义昭然。今乃曰穹苍予父也。名之曰上帝。以祭南郊。隤黄予母也。名之曰皇示。以祭北郊。阴阳配合。考妣并享。有若王与后妃之配体而匹尊。其蒙昧诬罔。慢天渎神。为何如者。夫法之出于二帝三王之经者。谓之经法何者。二帝三王。皆圣人也。圣人明理达物。故其所立法。皆合天理而协人纪。法之不出于二帝三王之经者。谓之坏法何者。驺衍吕不韦奸人也。王莽逆臣也。故秦之巫汉之纬。非儒者之所取也。北郊之祭而可言哉。〇又按北辰不知何物。若云北极。北极本无星点。若以耀魄宝为北辰。耀魄宝本一小星。其居亦少(一作小)偏。不当北极之枢纽。不免随天环转。以其近于北极。故其所转不离小圈之轮郭。不似赤道诸星之转于大圈。然若谓之恒居不动。非其实矣。藉使恒居不动。本一小星。了无灵识。万万非吾人所肯父事者。况昆崙者。西戎之山名。其大不过如我国之白头山。若以河源所出。谓其高峻为大地之最。则是又不达。流水绕地圆转之理。(详见余禹贡说)非圣人之通也。诸侯之礼。凡名山大川之不在其地者。不载祀典。以此推之。凡名山大川之不在神州之内者。非天子之所宜祭。楚虽不德。河非所望。何为而祭昆崙也。北郊之义。无所立矣。〔通典〕汉武帝即位曰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泽中。以高帝配帝。望拜如上帝礼。(从宽舒等议)〇宣帝间岁正月一日。至河东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东后土于长安北郊。(时丞相匡衡奏言祭地于北郊。则阴之象也。)〇平帝时王莽改祭礼。云天地有别有合。其合者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别者。冬日至祀南郊。高帝配。夏日至祀北郊。高后配。又奏旧称皇天上帝。今宜地祗称皇地后祗。〇光武中元二年。营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以配地祗。〇魏明帝时。诏方丘所祭。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〇高堂隆上表云(魏明帝之时)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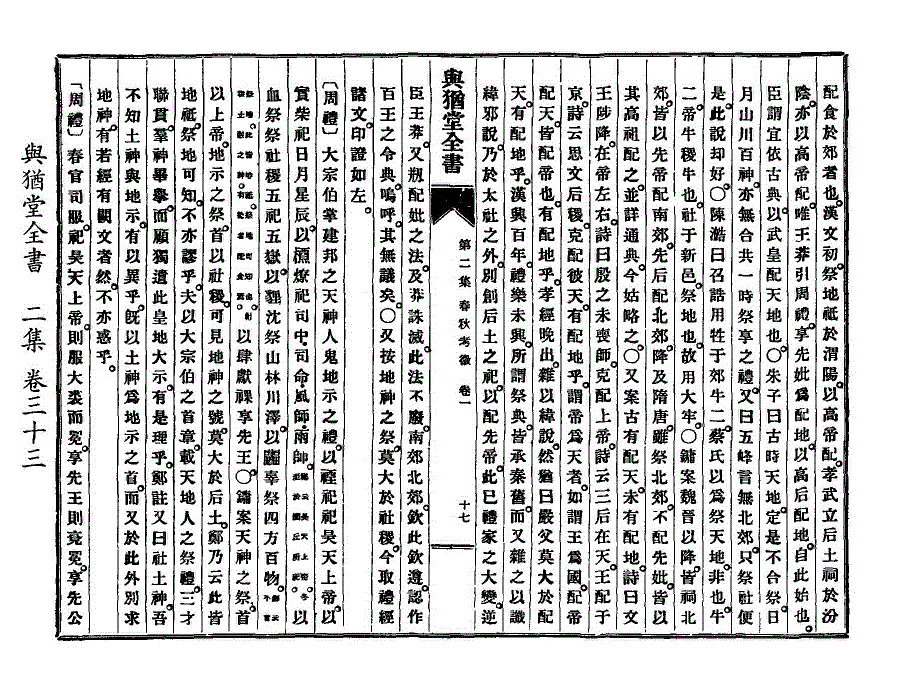 配食于郊者也。汉文初。祭地祗于渭阳。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地。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谓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〇朱子曰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合共一时祭享之礼。又曰五峰言无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说却好。〇陈浩曰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为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〇镛案魏晋以降。皆祠北郊。皆以先帝配南郊。先后配北郊。降及隋唐。虽祭北郊。不配先妣。皆以其高祖配之。并详通典。今姑略之。〇又案古有配天。未有配地。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有配地乎。谓帝为天者。如谓王为国。配帝配天。皆配帝也。有配地乎。孝经晚出。杂以纬说。然犹曰严父莫大于配天。有配地乎。汉兴百年。礼乐未兴。所谓祭典。皆承秦旧。而又杂之以谶纬邪说。乃于太社之外。别创后土之祀。以配先帝。此已礼家之大变。逆臣王莽。又创配妣之法。及莽诛灭。此法不废。南郊北郊。钦此钦遵。认作百王之令典。呜呼。其无议矣。〇又按地神之祭。莫大于社稷。今取礼经诸文。印證如左。
配食于郊者也。汉文初。祭地祗于渭阳。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地。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谓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〇朱子曰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合共一时祭享之礼。又曰五峰言无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说却好。〇陈浩曰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为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〇镛案魏晋以降。皆祠北郊。皆以先帝配南郊。先后配北郊。降及隋唐。虽祭北郊。不配先妣。皆以其高祖配之。并详通典。今姑略之。〇又案古有配天。未有配地。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有配地乎。谓帝为天者。如谓王为国。配帝配天。皆配帝也。有配地乎。孝经晚出。杂以纬说。然犹曰严父莫大于配天。有配地乎。汉兴百年。礼乐未兴。所谓祭典。皆承秦旧。而又杂之以谶纬邪说。乃于太社之外。别创后土之祀。以配先帝。此已礼家之大变。逆臣王莽。又创配妣之法。及莽诛灭。此法不废。南郊北郊。钦此钦遵。认作百王之令典。呜呼。其无议矣。〇又按地神之祭。莫大于社稷。今取礼经诸文。印證如左。〔周礼〕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副辜祭四方百物。(郑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祗。祭地可知也。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以肆献祼享先王。〇镛案天神之祭。首以上帝。地示之祭。首以社稷。可见地神之号。莫大于后土。郑乃云此皆地祗。祭地可知。不亦谬乎。夫以大宗伯之首章。载天地人之祭礼。三才联贯。群神毕举。而顾独遗此皇地大示。有是理乎。郑注又曰社土神。吾不知土神与地示。有以异乎。既以土神为地示之首。而又于此外别求地神。有若经有阙文者然。不亦惑乎。
〔周礼〕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兖(一作衮)冕。享先公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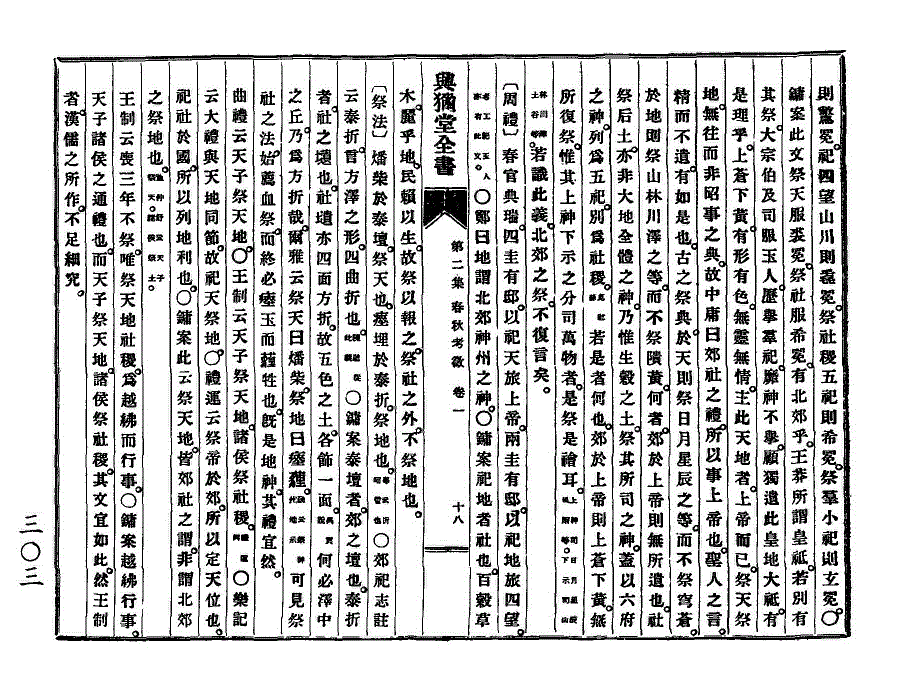 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〇镛案此文祭天服裘冕。祭社服希冕。有北郊乎。王莽所谓皇祗。若别有其祭。大宗伯及司服玉人。历举群祀。靡神不举。顾独遗此皇地大祗。有是理乎。上苍下黄。有形有色。无灵无情。主此天地者。上帝而已。祭天祭地。无往而非昭事之典。故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圣人之言。精而不遗。有如是也。古之祭典。于天则祭日月星辰之等。而不祭穹苍。于地则祭山林川泽之等。而不祭隤黄。何者。郊于上帝则无所遗也。社祭后土。亦非大地全体之神。乃惟生谷之土。祭其所司之神。盖以六府之神。列为五祀。别为社稷。(见社条)若是者何也。郊于上帝则上苍下黄。无所复祭。惟其上神下示之分司万物者。是祭是禬耳。(上神司日月星辰风雨等。下示司山林川泽土谷等。)若识此义。北郊之祭。不复言矣。
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〇镛案此文祭天服裘冕。祭社服希冕。有北郊乎。王莽所谓皇祗。若别有其祭。大宗伯及司服玉人。历举群祀。靡神不举。顾独遗此皇地大祗。有是理乎。上苍下黄。有形有色。无灵无情。主此天地者。上帝而已。祭天祭地。无往而非昭事之典。故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圣人之言。精而不遗。有如是也。古之祭典。于天则祭日月星辰之等。而不祭穹苍。于地则祭山林川泽之等。而不祭隤黄。何者。郊于上帝则无所遗也。社祭后土。亦非大地全体之神。乃惟生谷之土。祭其所司之神。盖以六府之神。列为五祀。别为社稷。(见社条)若是者何也。郊于上帝则上苍下黄。无所复祭。惟其上神下示之分司万物者。是祭是禬耳。(上神司日月星辰风雨等。下示司山林川泽土谷等。)若识此义。北郊之祭。不复言矣。〔周礼〕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考工记玉人亦有此文。)〇郑曰地谓北郊神州之神。〇镛案祀地者社也。百谷草木。丽乎地。民赖以生。故祭以报之。祭社之外。不祭地也。
〔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郑云折。昭晢也。)〇郊祀志注云泰折。言方泽之形。四曲折也。(陈浩从此义)〇镛案泰坛者。郊之坛也。泰折者。社之壝也。社壝亦四面方折。故五色之土。各饰一面。(禹贡说)何必泽中之丘。乃为方折哉。尔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疏云祭神州地示)可见祭社之法。始荐血祭。而终必瘗玉而薶牲也。既是地神。其礼宜然。
曲礼云天子祭天地。〇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礼运同)〇乐记云大礼与天地同节。故祀天祭地。〇礼运云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〇镛案此云祭天地。皆郊社之谓。非谓北郊之祭地也。(董仲舒云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王制云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〇镛案越绋行事。天子诸侯之通礼也。而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其文宜如此。然王制者。汉儒之所作。不足细究。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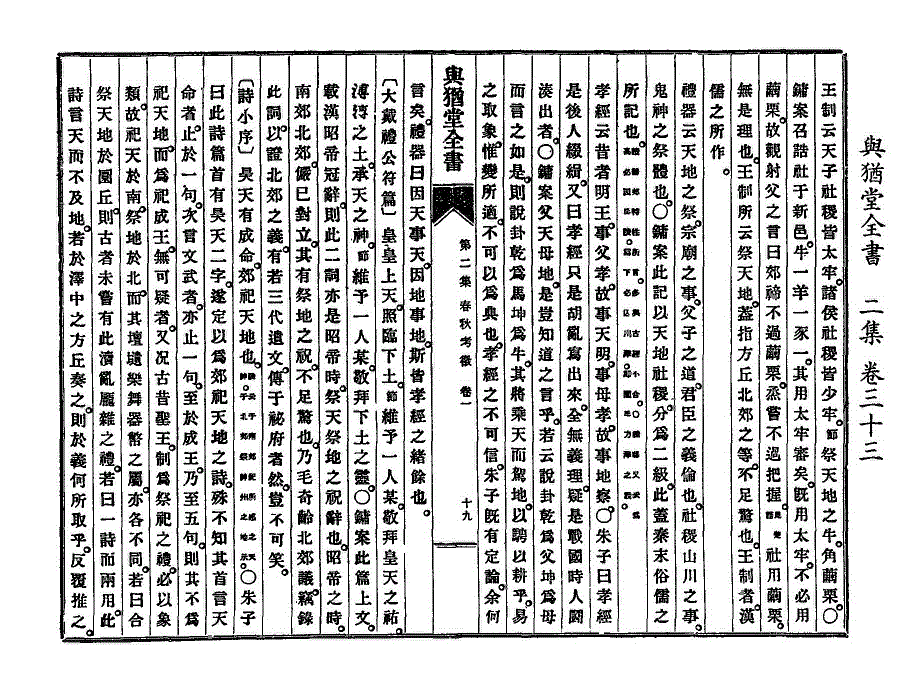 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节)祭天地之牛。角茧栗。〇镛案召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其用太牢审矣。既用太牢。不必用茧栗。故观射父之言曰郊禘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把握。(见楚语)社用茧栗。无是理也。王制所云祭天地。盖指方丘北郊之等。不足惊也。王制者。汉儒之所作。
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节)祭天地之牛。角茧栗。〇镛案召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其用太牢审矣。既用太牢。不必用茧栗。故观射父之言曰郊禘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把握。(见楚语)社用茧栗。无是理也。王制所云祭天地。盖指方丘北郊之等。不足惊也。王制者。汉儒之所作。礼器云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〇镛案此记以天地社稷。分为二级。此盖秦末俗儒之所记也。(礼器郊特牲所言。多与古经不合。〇礼器又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即圜丘方泽之说。)
孝经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〇朱子曰孝经是后人缀缉。又曰孝经只是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〇镛案父天母地。是岂知道之言乎。若云说卦乾为父坤为母而言之如是。则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其将乘天而驾地。以骋以耕乎。易之取象。惟变所适。不可以为典也。孝经之不可信。朱子既有定论。余何言矣。礼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斯皆孝经之绪馀也。
〔大戴礼公符篇〕皇皇上天。照临下土。(节)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溥溥之土。承天之神。(节)维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灵。〇镛案此篇上文。载汉昭帝冠辞。则此二词亦是昭帝时。祭天祭地之祝辞也。昭帝之时。南郊北郊。俨已对立。其有祭地之祝。不足惊也。乃毛奇龄北郊议。窃录此词。以證北郊之义。有若三代遗文。传于秘府者然。岂不可笑。
〔诗小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云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于北郊祭神州之地示。)〇朱子曰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乃至五句。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又况古昔圣王。制为祭祀之礼。必以象类。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坛壝乐舞器币之属。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则古者未尝有此渎乱庞杂之礼。若曰一诗而两用。此诗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则于义何所取乎。反覆推之。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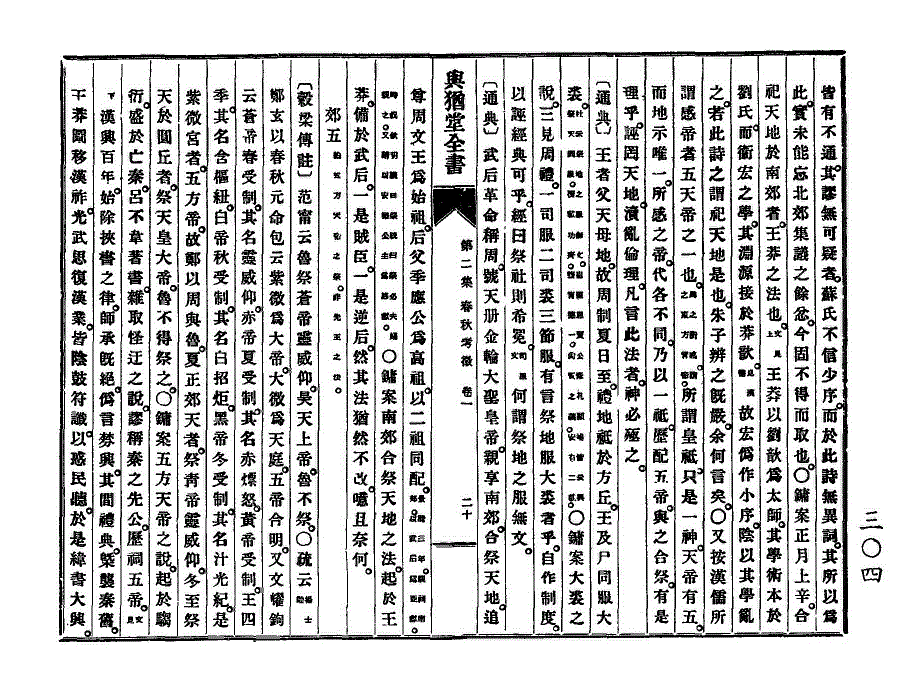 皆有不通。其谬无可疑者。苏氏不信少(一作小)序。而于此诗无异词。其所以为此。实未能忘北郊集议之馀忿。今固不得而取也。〇镛案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者。王莽之法也。(文见上)王莽以刘歆为太师。其学术本于刘氏。而卫宏之学。其渊源接于莽歆。(见汉书)故宏伪作小序。阴以其学乱之。若此诗之谓祀天地是也。朱子辨之既严。余何言矣。〇又按汉儒所谓感帝者五天帝之一也。(周之所感。谓之东方青帝。)所谓皇祗。只是一神。天帝有五。而地示唯一。所感之帝。代各不同。乃以一祗。历配五帝。与之合祭。有是理乎。诬罔天地。渎乱伦理。凡言此法者。神必殛之。
皆有不通。其谬无可疑者。苏氏不信少(一作小)序。而于此诗无异词。其所以为此。实未能忘北郊集议之馀忿。今固不得而取也。〇镛案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者。王莽之法也。(文见上)王莽以刘歆为太师。其学术本于刘氏。而卫宏之学。其渊源接于莽歆。(见汉书)故宏伪作小序。阴以其学乱之。若此诗之谓祀天地是也。朱子辨之既严。余何言矣。〇又按汉儒所谓感帝者五天帝之一也。(周之所感。谓之东方青帝。)所谓皇祗。只是一神。天帝有五。而地示唯一。所感之帝。代各不同。乃以一祗。历配五帝。与之合祭。有是理乎。诬罔天地。渎乱伦理。凡言此法者。神必殛之。〔通典〕王者父天母地。故周制夏日至。礼地祗于方丘。王及尸同服大裘。(杜云祭地之服无文。崔灵恩贾公彦孔颖达皆云与祭天同服。覆载功齐。煦育德一。尚质之义。安有二哉。)〇镛案大裘之说。三见周礼。一司服二司裘三节服。有言祭地服大裘者乎。自作制度。以诬经典可乎。经曰祭社则希冕。(司服文)何谓祭地之服无文。
〔通典〕武后革命称周。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为始祖。后父季应公为高祖。以二祖同配。(景龙三年。亲祠南郊。以武后为亚献。时祝钦明议曰祭统曰祭必夫妇亲之。又请以安乐公主为终献。)〇镛案南郊合祭天地之法。起于王莽。备于武后。一是贼臣。一是逆后。然其法犹然不改。噫且奈何。
郊五(论五方天帝之祭。非先王之法。)
〔谷梁传注〕范宁云鲁祭苍帝灵威仰。昊天上帝。鲁不祭。〇疏云 扬(一作杨)士勋 郑玄以春秋元命包云紫微为大帝。大微为天庭。五帝合明。又文耀钩云苍帝春受制。其名灵威仰。赤帝夏受制。其名赤熛怒。黄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枢纽。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炬。黑帝冬受制。其名汁光纪。是紫微宫者。五方帝。故郑以周与鲁。夏正郊天者。祭青帝灵威仰。冬至祭天于圆丘者。祭天皇大帝。鲁不得祭之。〇镛案五方天帝之说。起于驺衍。盛于亡秦。吕不韦著书。杂取怪迂之说。谬称秦之先公。历祠五帝。(文见下)汉兴百年。始除挟书之律。师承既绝。伪言棼兴。其间礼典。槩袭秦旧。王莽图移汉祚。光武思复汉业。皆阴鼓符谶。以惑民听。于是纬书大兴。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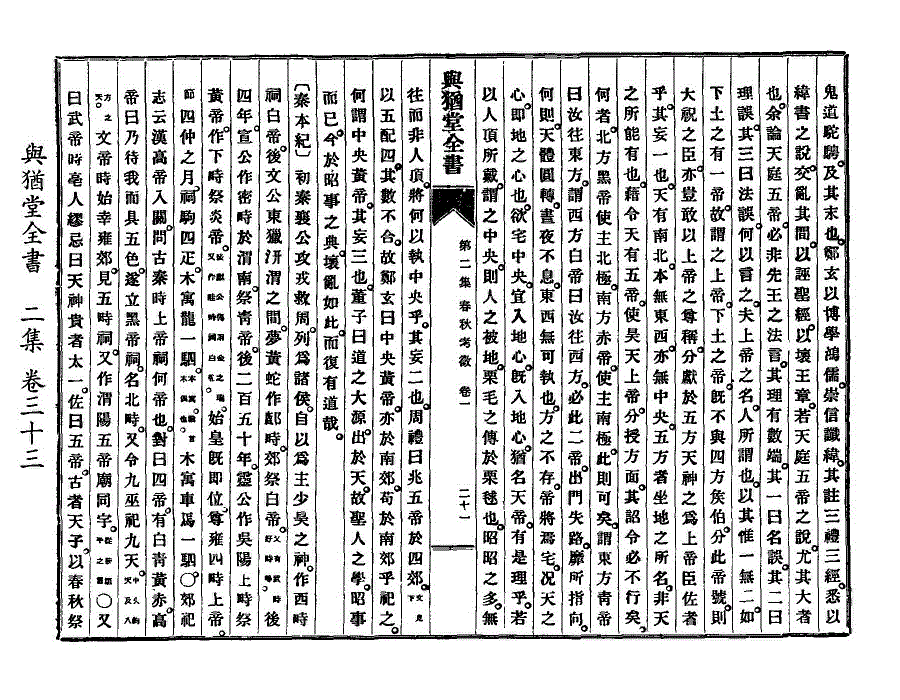 鬼道驼骋。及其末也。郑玄以博学鸿儒。崇信谶纬。其注三礼三经。悉以纬书之说。交乱其间。以诬圣经。以坏王章。若天庭五帝之说。尤其大者也。余论天庭五帝。必非先王之法言。其理有数端。其一曰名误。其二曰理误。其三曰法误。何以言之。夫上帝之名。人所谓也。以其惟一无二。如下土之有一帝。故谓之上帝。下土之帝。既不与四方侯伯。分此帝号。则大祝之臣。亦岂敢以上帝之尊称。分献于五方天神之为上帝臣佐者乎。其妄一也。天有南北。本无东西。亦无中央。五方者坐地之所名。非天之所能有也。藉令天有五帝。使昊天上帝。分授方面。其诏令必不行矣。何者。北方黑帝使主北极。南方赤帝。使主南极。此则可矣。谓东方青帝曰汝往东方。谓西方白帝曰汝往西方。必此二帝。出门失路。靡所指向。何则。天体圆转。昼夜不息。东西无可执也。方之不存。帝将焉宅。况天之心。即地之心也。欲宅中央。宜入地心。既入地心。犹名天帝。有是理乎。若以人顶所戴。谓之中央。则人之被地。주-D002栗毛之传于栗毬也。昭昭之多。无往而非人顶。将何以执中央乎。其妄二也。周礼曰兆五帝于四郊。(文见下)以五配四。其数不合。故郑玄曰中央黄帝。亦于南郊。苟于南郊乎祀之何谓中央黄帝。其妄三也。董子曰道之大源。出于天。故圣人之学。昭事而已。今于昭事之典。坏乱如此。而复有道哉。
鬼道驼骋。及其末也。郑玄以博学鸿儒。崇信谶纬。其注三礼三经。悉以纬书之说。交乱其间。以诬圣经。以坏王章。若天庭五帝之说。尤其大者也。余论天庭五帝。必非先王之法言。其理有数端。其一曰名误。其二曰理误。其三曰法误。何以言之。夫上帝之名。人所谓也。以其惟一无二。如下土之有一帝。故谓之上帝。下土之帝。既不与四方侯伯。分此帝号。则大祝之臣。亦岂敢以上帝之尊称。分献于五方天神之为上帝臣佐者乎。其妄一也。天有南北。本无东西。亦无中央。五方者坐地之所名。非天之所能有也。藉令天有五帝。使昊天上帝。分授方面。其诏令必不行矣。何者。北方黑帝使主北极。南方赤帝。使主南极。此则可矣。谓东方青帝曰汝往东方。谓西方白帝曰汝往西方。必此二帝。出门失路。靡所指向。何则。天体圆转。昼夜不息。东西无可执也。方之不存。帝将焉宅。况天之心。即地之心也。欲宅中央。宜入地心。既入地心。犹名天帝。有是理乎。若以人顶所戴。谓之中央。则人之被地。주-D002栗毛之传于栗毬也。昭昭之多。无往而非人顶。将何以执中央乎。其妄二也。周礼曰兆五帝于四郊。(文见下)以五配四。其数不合。故郑玄曰中央黄帝。亦于南郊。苟于南郊乎祀之何谓中央黄帝。其妄三也。董子曰道之大源。出于天。故圣人之学。昭事而已。今于昭事之典。坏乱如此。而复有道哉。〔秦本纪〕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后文公东猎汧渭之间。梦黄蛇作鄜畤。郊祭白帝。(又有武畤好畤等。)后四年。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后二百五十年。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献公得雨金之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始皇既即位。尊雍四畤上帝。(节)四仲之月。祠驹四疋。木寓龙一驷。本(一作木)寓。犹言木偶也。 木寓车马一驷。〇郊祀志云汉高帝入关。问古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又令九巫祀九天。(中央钧天及八方之天。)文帝时始幸雍郊。见五畤祠。又作渭阳五帝庙同宇。(从新垣平之言)〇又曰武帝时亳人缪忌曰天神贵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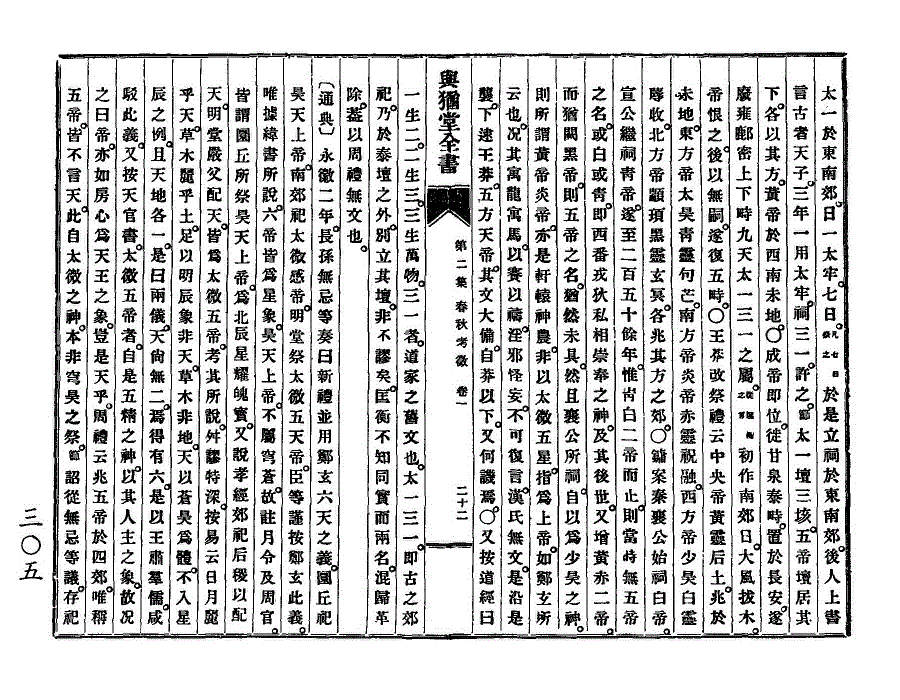 太一于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之)于是立祠于东南郊。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许之。(节)太一坛三垓。五帝坛居其下。各以其方。黄帝于西南未地。〇成帝即位。徙甘泉泰畤。置于长安。遂废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之属。(从匡衡之言)初作南郊日。大风拔木。帝恨之。后以无嗣。遂复五畤。〇王莽改祭礼云中央帝黄灵后土。兆于未地。东方帝太昊青灵句芒。南方帝炎帝赤灵祝融。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各兆其方之郊。〇镛案秦襄公始祠白帝。宣公继祠青帝。遂至二百五十馀年。惟青白二帝而止。则当时无五帝之名。或白或青。即西番戎狄私相崇奉之神。及其后世。又增黄赤二帝。而犹阙黑帝。则五帝之名。犹然未具。然且襄公所祠。自以为少昊之神。则所谓黄帝炎帝。亦是轩辕神农。非以太微五星。指为上帝。如郑玄所云也。况其寓龙寓马。以赛以祷。淫邪怪妄。不可复言。汉氏无文。是沿是袭。下逮王莽。五方天帝。其文大备。自莽以下。又何讥焉。〇又按道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一者。道家之旧文也。太一三一。即古之郊祀。乃于泰坛之外。别立其坛。非不谬矣。匡衡不知同实而两名。混归革除。盖以周礼无文也。
太一于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之)于是立祠于东南郊。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许之。(节)太一坛三垓。五帝坛居其下。各以其方。黄帝于西南未地。〇成帝即位。徙甘泉泰畤。置于长安。遂废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之属。(从匡衡之言)初作南郊日。大风拔木。帝恨之。后以无嗣。遂复五畤。〇王莽改祭礼云中央帝黄灵后土。兆于未地。东方帝太昊青灵句芒。南方帝炎帝赤灵祝融。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各兆其方之郊。〇镛案秦襄公始祠白帝。宣公继祠青帝。遂至二百五十馀年。惟青白二帝而止。则当时无五帝之名。或白或青。即西番戎狄私相崇奉之神。及其后世。又增黄赤二帝。而犹阙黑帝。则五帝之名。犹然未具。然且襄公所祠。自以为少昊之神。则所谓黄帝炎帝。亦是轩辕神农。非以太微五星。指为上帝。如郑玄所云也。况其寓龙寓马。以赛以祷。淫邪怪妄。不可复言。汉氏无文。是沿是袭。下逮王莽。五方天帝。其文大备。自莽以下。又何讥焉。〇又按道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一者。道家之旧文也。太一三一。即古之郊祀。乃于泰坛之外。别立其坛。非不谬矣。匡衡不知同实而两名。混归革除。盖以周礼无文也。〔通典〕永徽二年。长孙无忌等奏曰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帝(一作天)皆为星象。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圜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耀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易云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土。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按天官书。太微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以其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节)诏从无忌等议。存祀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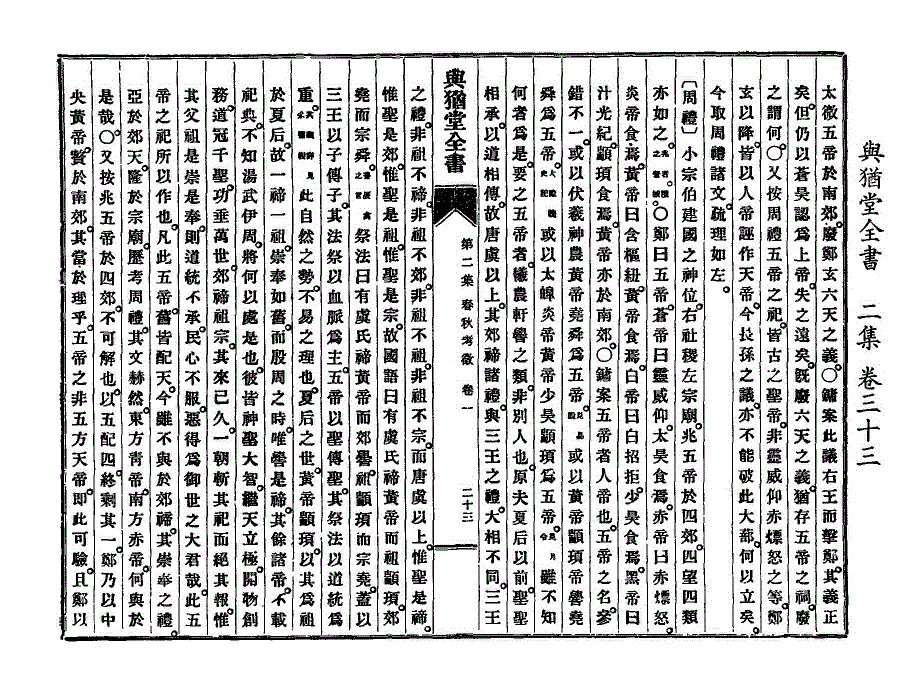 太微五帝于南郊。废郑玄六天之义。〇镛案此议右王而击郑。其义正矣。但仍以苍昊认为上帝。失之远矣。既废六天之义。犹存五帝之祠。废之谓何。〇又按周礼五帝之祀。皆古之圣帝。非灵威仰赤熛怒之等。郑玄以降。皆以人帝诬作天帝。今长孙之议。亦不能破此大蔀。何以立矣。今取周礼诸文。疏理如左。
太微五帝于南郊。废郑玄六天之义。〇镛案此议右王而击郑。其义正矣。但仍以苍昊认为上帝。失之远矣。既废六天之义。犹存五帝之祠。废之谓何。〇又按周礼五帝之祀。皆古之圣帝。非灵威仰赤熛怒之等。郑玄以降。皆以人帝诬作天帝。今长孙之议。亦不能破此大蔀。何以立矣。今取周礼诸文。疏理如左。〔周礼〕小宗伯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者。坛之营域。)〇郑曰五帝。苍帝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帝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帝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帝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帝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〇镛案五帝者人帝也。五帝之名。参错不一。或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见易说)或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大戴礼史记)或以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见月令)虽不知何者为是。要之五帝者。牺农轩喾之类。非别人也。原夫夏后以前。圣圣相承。以道相传。故唐虞以上。其郊禘诸礼。与三王之礼。大相不同。三王之礼。非祖不禘。非祖不郊。非祖不祖。非祖不宗。而唐虞以上。惟圣是禘。惟圣是郊。惟圣是祖。惟圣是宗。故国语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鲁展禽之言)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盖以三王以子传子。其法祭(祭法)以血脉为主。五帝以圣传圣。其祭法以道统为重。(其义详见余书说)此自然之势。不易之理也。夏后之世。黄帝颛顼。以其为祖于夏后。故一禘一祖。崇奉如旧。而殷周之时。唯喾是禘。其馀诸帝。不载祀典。不知汤武伊周。将何以处是也。彼皆神圣大智。继天立极。开物创务。道冠千圣。功垂万世。郊禘祖宗。其来已久。一朝斩其祀而绝其报。惟其父祖是崇是奉。则道统不承。民心不服。恶得为御世之大君哉。此五帝之祀所以作也。凡此五帝。旧皆配天。今虽不与于郊禘。其崇奉之礼。亚于郊天。隆于宗庙。历考周礼。其文赫然。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何与于是哉。〇又按兆五帝于四郊。不可解也。以五配四。终剩其一。郑乃以中央黄帝。赘于南郊。其当于理乎。五帝之非五方天帝。即此可验。且郑以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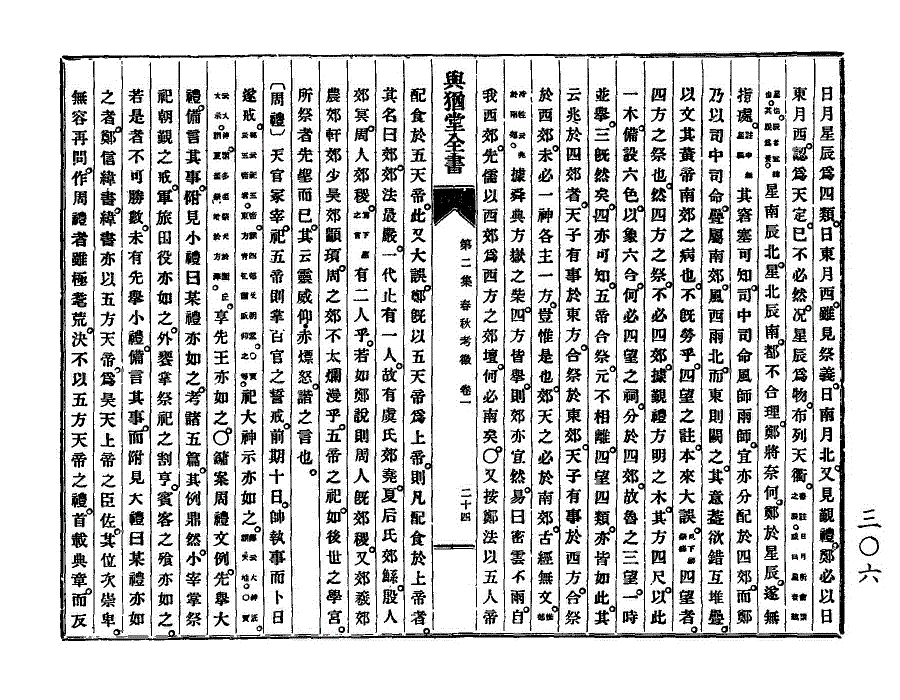 日月星辰为四类。日东月西。虽见祭义。日南月北。又见觐礼。郑必以日东月西。认为天定。已不必然。况星辰为物。布列天衢。书注日月所会谓之辰。或曰星者经(一作五)星也。辰者五纬주-D007也。其说为长。 星南辰北。星北辰南。都不合理。郑将奈何。郑于星辰。遂无指处。(注中无星辰)其窘塞可知。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宜亦分配于四郊。而郑乃以司中司命。叠属南郊。风西雨北。而东则阙之。其意盖欲错互堆叠。以文其黄帝南郊之病也。不既劳乎。四望之注。本来大误。(见下望祭条)四望者。四方之祭也。然四方之祭。不必四郊。据觐礼方明之木。其方四尺。以此一木。备设六色。以象六合。何必四望之祠。分于四郊。故鲁之三望。一时并举。三既然矣。四亦可知。五帝合祭。元不相离。四望四类。亦皆如此。其云兆于四郊者。天子有事于东方。合祭于东郊。天子有事于西方。合祭于西郊。未必一神各主一方。岂惟是也。郊天之必于南郊。古经无文。(惟郊特牲云兆于南郊。)据舜典方岳之柴。四方皆举。则郊亦宜然。易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先儒以西郊为西方之郊坛。何必南矣。〇又按郑法(一作玄)以五人帝配食于五天帝。此又大误。郑既以五天帝为上帝。则凡配食于上帝者。其名曰郊。郊法最严。一代止有一人。故有虞氏郊尧。夏后氏郊鲧。殷人郊冥。周人郊稷。(柳下惠之言)有二人乎。若如郑说则周人既郊稷。又郊羲郊农郊轩郊少昊郊颛顼。周之郊不太烂漫乎。五帝之祀。如后世之学宫。所祭者先圣而已。其云灵威仰、赤熛怒。谐之言也。
日月星辰为四类。日东月西。虽见祭义。日南月北。又见觐礼。郑必以日东月西。认为天定。已不必然。况星辰为物。布列天衢。书注日月所会谓之辰。或曰星者经(一作五)星也。辰者五纬주-D007也。其说为长。 星南辰北。星北辰南。都不合理。郑将奈何。郑于星辰。遂无指处。(注中无星辰)其窘塞可知。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宜亦分配于四郊。而郑乃以司中司命。叠属南郊。风西雨北。而东则阙之。其意盖欲错互堆叠。以文其黄帝南郊之病也。不既劳乎。四望之注。本来大误。(见下望祭条)四望者。四方之祭也。然四方之祭。不必四郊。据觐礼方明之木。其方四尺。以此一木。备设六色。以象六合。何必四望之祠。分于四郊。故鲁之三望。一时并举。三既然矣。四亦可知。五帝合祭。元不相离。四望四类。亦皆如此。其云兆于四郊者。天子有事于东方。合祭于东郊。天子有事于西方。合祭于西郊。未必一神各主一方。岂惟是也。郊天之必于南郊。古经无文。(惟郊特牲云兆于南郊。)据舜典方岳之柴。四方皆举。则郊亦宜然。易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先儒以西郊为西方之郊坛。何必南矣。〇又按郑法(一作玄)以五人帝配食于五天帝。此又大误。郑既以五天帝为上帝。则凡配食于上帝者。其名曰郊。郊法最严。一代止有一人。故有虞氏郊尧。夏后氏郊鲧。殷人郊冥。周人郊稷。(柳下惠之言)有二人乎。若如郑说则周人既郊稷。又郊羲郊农郊轩郊少昊郊颛顼。周之郊不太烂漫乎。五帝之祀。如后世之学宫。所祭者先圣而已。其云灵威仰、赤熛怒。谐之言也。〔周礼〕天官冢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郑云祀五帝。谓四郊及明堂。〇贾云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之等。)祀大神示亦如之。(郑云大神祗。谓天地。〇贾云大神。谓冬至祭天于圜丘。大示。谓夏至祭地于方泽。)享先王亦如之。〇镛案周礼文例。先举大礼。备言其事。附见小礼曰某礼亦如之。考诸五篇。其例鼎然。小宰掌祭祀朝觐之戒。军旅田役亦如之。外饔掌祭祀之割亨。宾客之飧亦如之。若是者不可胜数。未有先举小礼。备言其事。而附见大礼曰某礼亦如之者。郑信纬书。纬书亦以五方天帝。为昊天上帝之臣佐。其位次崇卑。无容再问。作周礼者虽极耄荒。决不以五方天帝之礼。首载典章。而反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7H 页
 以昊天上帝之礼。附见其末。今注疏之说如此。不亦谬乎。经文首举五帝者。以郊天之祭。更尊更严。或者三公掌其誓戒。非冢宰之所得为。故自五帝以下也。礼曰卜郊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郊特牲)天子之尊而亲听誓命。则其誓其戒。岂卿宰之所得为哉。必太师太傅之等。方可以为此。故六官之职。无此说也。〇又按大神者。日月司命之等也。大示者。社稷五岳之类也。其秩皆亚于五帝。故附见其礼曰亦如之也。
以昊天上帝之礼。附见其末。今注疏之说如此。不亦谬乎。经文首举五帝者。以郊天之祭。更尊更严。或者三公掌其誓戒。非冢宰之所得为。故自五帝以下也。礼曰卜郊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郊特牲)天子之尊而亲听誓命。则其誓其戒。岂卿宰之所得为哉。必太师太傅之等。方可以为此。故六官之职。无此说也。〇又按大神者。日月司命之等也。大示者。社稷五岳之类也。其秩皆亚于五帝。故附见其礼曰亦如之也。〔周礼〕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〇郑曰大旅上帝。祭于圜丘。国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皇邸。如今之屏风。)五帝五色之帝。〇镛案郑尝以圜丘奏乐之礼。谓之禘祭。(大司乐之注)今乃以是谓之旅祭。其言之横走溃裂如此。而可准乎。大宗伯明云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尚有说乎。〇又按此文五帝。明是人帝。非天帝也。其旅上帝则上无幕帟。其祀五帝则大幄小幄。又设重帟。盖以祭天之礼。下惟扫地。上不蔽天。故张毡案设皇邸而已。五帝之祀。其礼多文。故幄帟重叠也。诚若天帝。顾当如是乎。
〔周礼〕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〇郑曰上帝五帝也。〇镛案天官掌次。明云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重帟。八字打开。两峰对峙。郑乃曰旅上帝即祀五帝。不亦耄乎。其说之跋前疐后。类皆如此。
〔周礼〕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考工记玉人。亦有此文。)〇郑曰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殊言帝(一作天)者。尊异之也。〇镛案祀天者郊也。祀地者社也。此是正祭。故但言祀天祀地。至于旅之为礼。非祭非祈。故经皆别言。典瑞章云大祭大旅。共其玉器。旅之非祭。亦已明矣。旅与胪通。(或作旅作胪)旅者陈也。诗云殽核维旅。礼曰旅币无方。旅者陈也。(大宗伯注云陈其祭祀以祈焉。礼不如祀之备也。)敷陈事实。以告帝也。故曰国有大故则旅上帝。旅四望。告急之义也。(如今之告由祭)故明其所向。别言上帝。非谓祀天旅주-D010所向不同也。秦汉以来。祭天祭帝。分而二之。故孝经亦以配天配帝。分为二事。此孝经所以见疑于朱子也。稽之古经。未尝如此。旅上帝之上帝。岂所谓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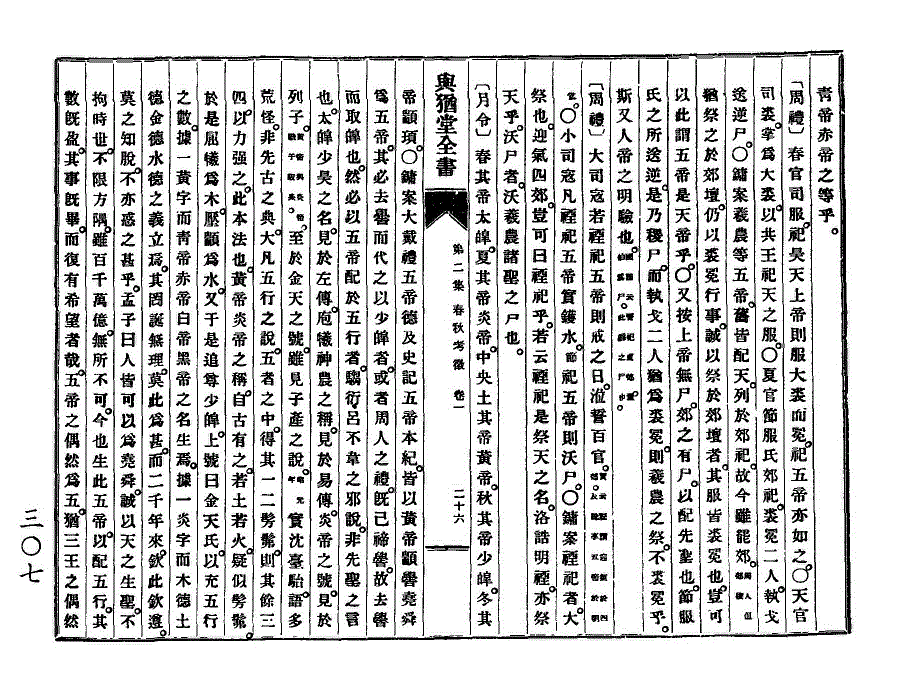 青帝赤帝之等乎。
青帝赤帝之等乎。〔周礼〕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〇天官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〇夏官节服氏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〇镛案羲农等五帝。旧皆配天。列于郊祀。故今虽罢郊。(周人但郊稷)犹祭之于郊坛。仍以裘冕行事。诚以祭于郊坛者。其服皆裘冕也。岂可以此谓五帝是天帝乎。〇又按上帝无尸。郊之有尸。以配先圣也。节服氏之所送逆。是乃稷尸。而执戈二人犹为裘冕。则羲农之祭。不裘冕乎。斯又人帝之明验也。(国语云晋祀夏郊。董伯为尸。此鲧之尸也。)
〔周礼〕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则戒之日。涖誓百官。(贾云禋谓迎气于四郊。及总享五帝于明堂。)〇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实镬水。(节)祀五帝则沃尸。〇镛案禋祀者。大祭也。迎气四郊。岂可曰禋祀乎。若云禋祀是祭天之名。洛诰明禋。亦祭天乎。沃尸者。沃羲农诸圣之尸也。
〔月令〕春其帝太皞。夏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秋其帝少皞。冬其帝颛顼。〇镛案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皆以黄帝颛喾尧舜为五帝。其必去喾而代之以少皞者。或者周人之礼。既已禘喾。故去喾而取皞也。然必以五帝配于五行者。驺衍、吕不韦之邪说。非先圣之言也。太皞少昊之名。见于左传。庖牺神农之称。见于易传。炎帝之号。见于列子。(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至于金天之号。虽见子产之说。(昭元年)实沈台骀。语多荒怪。非先古之典。大凡五行之说。五者之中。得其一二髣髴。则其馀三四。以力强之。此本法也。黄帝炎帝之称。自古有之。若土若火。疑似髣髴于是屈牺为木。压颛为水。又于是追尊少皞。上号曰金天氏。以充五行之数。据一黄字而青帝赤帝白帝黑帝之名生焉。据一炎字而木德土德金德水德之义立焉。其罔诞无理。莫此为甚。而二千年来。钦此钦遵。莫之知脱。不亦惑之甚乎。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诚以天之生圣。不拘时世。不限方隅。虽百千万亿。无所不可。今也生此五帝。以配五行。其数既盈。其事既毕。而复有希望者哉。五帝之偶然为五。犹三王之偶然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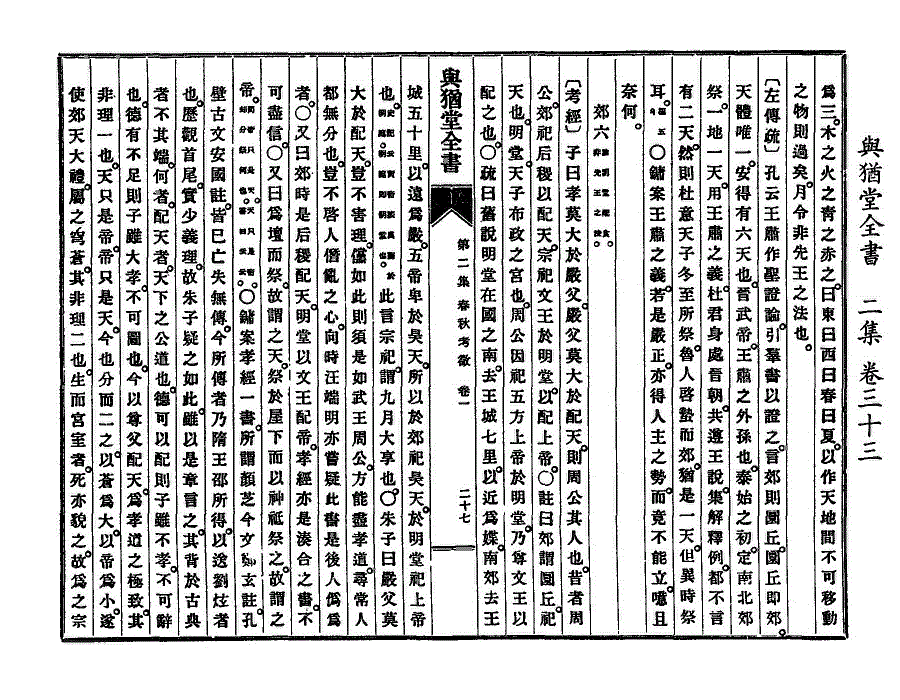 为三。木之火之青之赤之。曰东曰西曰春曰夏。以作天地间不可移动之物则过矣。月令非先王之法也。
为三。木之火之青之赤之。曰东曰西曰春曰夏。以作天地间不可移动之物则过矣。月令非先王之法也。〔左传疏〕孔云王肃作圣證论。引群书以證之。言郊则圜丘。圜丘即郊。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晋武帝。王肃之外孙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肃之义。杜君身处晋朝。共遵王说。集解释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则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启蛰而郊。犹是一天。但异时祭耳。(桓五年)〇镛案王肃之义。若是严正。亦得人主之势。而竟不能立。噫且奈何。
郊六(论明堂配食。非先王之法。)
〔考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〇注曰郊谓圜丘。祀天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〇疏曰旧说明堂在国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为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远为严。五帝卑于昊天。所以于郊祀昊天。于明堂祀上帝也。(史记云黄帝接万灵于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此言宗祀。谓九月大享也。〇朱子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岂不害理。傥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也。岂不启人僭乱之心。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〇又曰郊时是后稷配天。明堂以文王配帝。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〇又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谓之帝。(问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答曰云云。)〇镛案孝经一书。所谓颜芝今文郑玄注。孔壁古文安国注。皆已亡失无传。今所传者乃隋王邵所得。以送刘炫者也。历观首尾。实少义理。故朱子疑之如此。虽以是章言之。其背于古典者不주-D001其端。何者。配天者。天下之公道也。德可以配则子虽不孝。不可辞也。德有不足则子虽大孝。不可图也。今以尊父配天。为孝道之极致。其非理一也。天只是帝。帝只是天。今也分而二之。以苍为大。以帝为小。遂使郊天大礼。属之穹苍。其非理二也。生而宫室者。死亦貌之。故为之宗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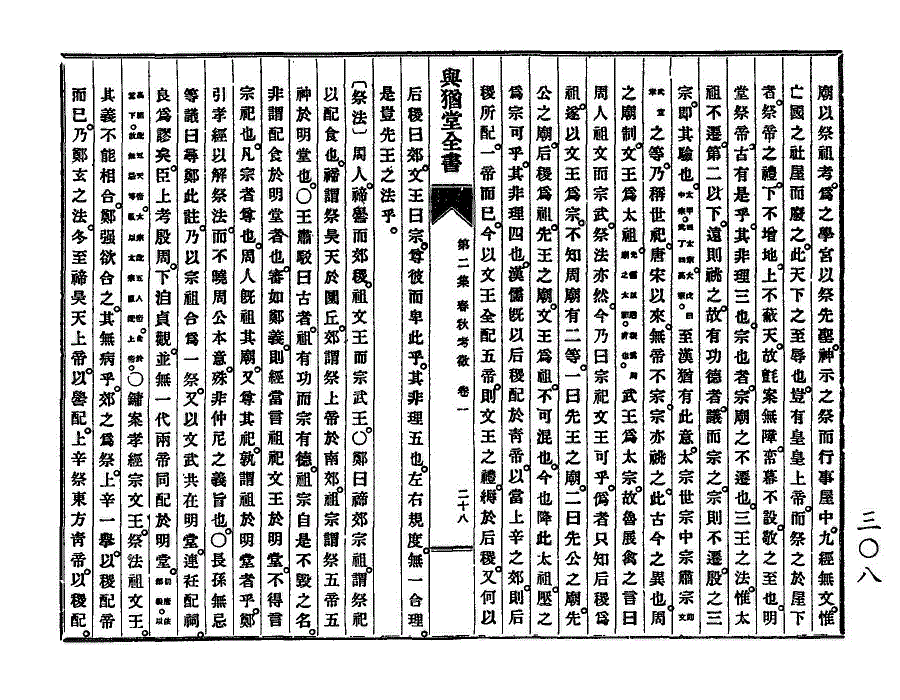 庙以祭祖考。为之学宫以祭先圣。神示之祭而行事屋中。九经无文。惟亡国之社屋而废之。此天下之至辱也。岂有皇皇上帝。而祭之于屋下者。祭帝之礼。下不增地。上不蔽天。故毡案无障。帟幕不设。敬之至也。明堂祭帝。古有是乎。其非理三也。宗也者。宗庙之不迁也。三王之法。惟太祖不迁。第二以下。远则祧之。故有功德者。议而宗之。宗则不迁。殷之三宗。即其验也。(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至汉犹有此意。太宗世宗中宗肃宗(即文武宣章)之等。乃称世祀。唐宋以来。无帝不宗。宗亦祧之。此古今之异也。周之庙制。文王为太祖。(先儒以后稷为周庙之太祖。非也。)武王为太宗。故鲁展禽之言曰周人祖文而宗武。祭法亦然。今乃曰宗祀文王可乎。伪者只知后稷为祖。遂以文王为宗。不知周庙有二等。一曰先王之庙。二曰先公之庙。先公之庙。后稷为祖。先王之庙。文王为祖。不可混也。今也降此太祖。压之为宗可乎。其非理四也。汉儒既以后稷配于青帝。以当上辛之郊。则后稷所配。一帝而已。今以文王全配五帝。则文王之礼。缛于后稷。又何以后稷曰郊。文王曰宗。尊彼而卑此乎。其非理五也。左右规度。无一合理。是岂先王之法乎。
庙以祭祖考。为之学宫以祭先圣。神示之祭而行事屋中。九经无文。惟亡国之社屋而废之。此天下之至辱也。岂有皇皇上帝。而祭之于屋下者。祭帝之礼。下不增地。上不蔽天。故毡案无障。帟幕不设。敬之至也。明堂祭帝。古有是乎。其非理三也。宗也者。宗庙之不迁也。三王之法。惟太祖不迁。第二以下。远则祧之。故有功德者。议而宗之。宗则不迁。殷之三宗。即其验也。(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至汉犹有此意。太宗世宗中宗肃宗(即文武宣章)之等。乃称世祀。唐宋以来。无帝不宗。宗亦祧之。此古今之异也。周之庙制。文王为太祖。(先儒以后稷为周庙之太祖。非也。)武王为太宗。故鲁展禽之言曰周人祖文而宗武。祭法亦然。今乃曰宗祀文王可乎。伪者只知后稷为祖。遂以文王为宗。不知周庙有二等。一曰先王之庙。二曰先公之庙。先公之庙。后稷为祖。先王之庙。文王为祖。不可混也。今也降此太祖。压之为宗可乎。其非理四也。汉儒既以后稷配于青帝。以当上辛之郊。则后稷所配。一帝而已。今以文王全配五帝。则文王之礼。缛于后稷。又何以后稷曰郊。文王曰宗。尊彼而卑此乎。其非理五也。左右规度。无一合理。是岂先王之法乎。〔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〇郑曰禘郊宗祖。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〇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〇长孙无忌等议曰寻郑此注。乃以宗祖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祠。良为谬矣。臣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初唐依郑义。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食于堂下。故无忌等议以太宗直配上帝。)镛案孝经宗文王。祭法祖文王。其义不能相合。郑强欲合之。其无病乎。郊之为祭。上辛一举。以稷配帝而已。乃郑玄之法。冬至禘昊天上帝。以喾配。上辛祭东方青帝。以稷配。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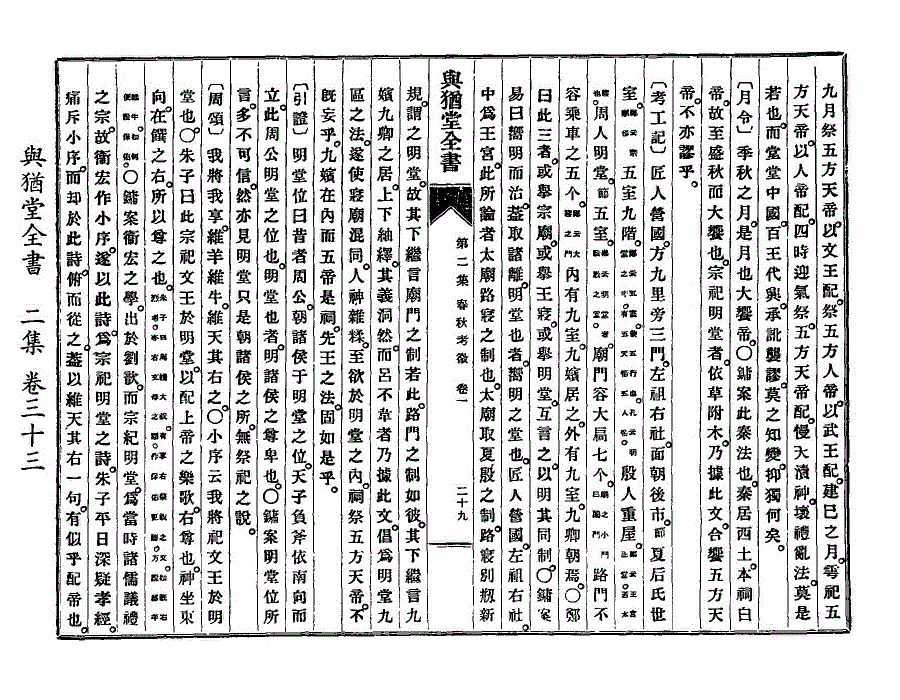 九月祭五方天帝。以文王配。祭五方人帝。以武王配。建巳之月。雩祀五方天帝。以人帝配。四时迎气。祭五方天帝。주-D002配。慢天渎神。坏礼乱法。莫是若也。而堂堂中国。百王代兴。承讹袭谬。莫之知变。抑独何矣。
九月祭五方天帝。以文王配。祭五方人帝。以武王配。建巳之月。雩祀五方天帝。以人帝配。四时迎气。祭五方天帝。주-D002配。慢天渎神。坏礼乱法。莫是若也。而堂堂中国。百王代兴。承讹袭谬。莫之知变。抑独何矣。〔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飨帝。〇镛案此秦法也。秦居西土。本祠白帝。故至盛秋而大飨也。宗祀明堂者。依草附木。乃据此文。合飨五方天帝。不亦谬乎。
〔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节)夏后氏世室。(郑云宗庙也)五室九阶。(郑云五室。象五行也。孔云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殷人重屋。(郑云王宫正堂。若太寝也。)周人明堂。(节)五室。(郑云明堂者。政教之堂。)庙门容大扃七个。(庙之小门曰闱门)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郑云大寝之门)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〇郑曰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〇镛案易曰向明而治。盖取诸离。明堂也者。向明之堂也。匠人营国。左祖右社。中为王宫。此所论者太庙路寝之制也。太庙取夏殷之制。路寝别创新规。谓之明堂。故其下继言庙门之制若此。路门之制如彼。其下继言九嫔九卿之居。上下䌷绎。其义洞然。而吕不韦者乃据此文。倡为明堂九区之法。遂使寝庙混同。人神杂糅。至欲于明堂之内。祠祭五方天帝。不既妄乎。九嫔在内而五帝是祠。先王之法。固如是乎。
〔引證〕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〇镛案明堂位所言。多不可信。然亦见明堂只是朝诸侯之所。无祭祀之说。
〔周颂〕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〇小序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〇朱子曰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乐歌。右。尊也。神坐东向。在馔之右。所以尊之也。(朱子曰周礼大祝。有享右祭祝之文。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类。作保佑更难。方说维羊维牛。如何便说保佑。)〇镛案卫宏之学。出于刘歆。而宗纪明堂。为当时诸儒议礼之宗。故卫宏作小序。遂以此诗。为宗祀明堂之诗。朱子平日深疑孝经。痛斥小序。而却于此诗。俯而从之。盖以维天其右一句。有似乎配帝也。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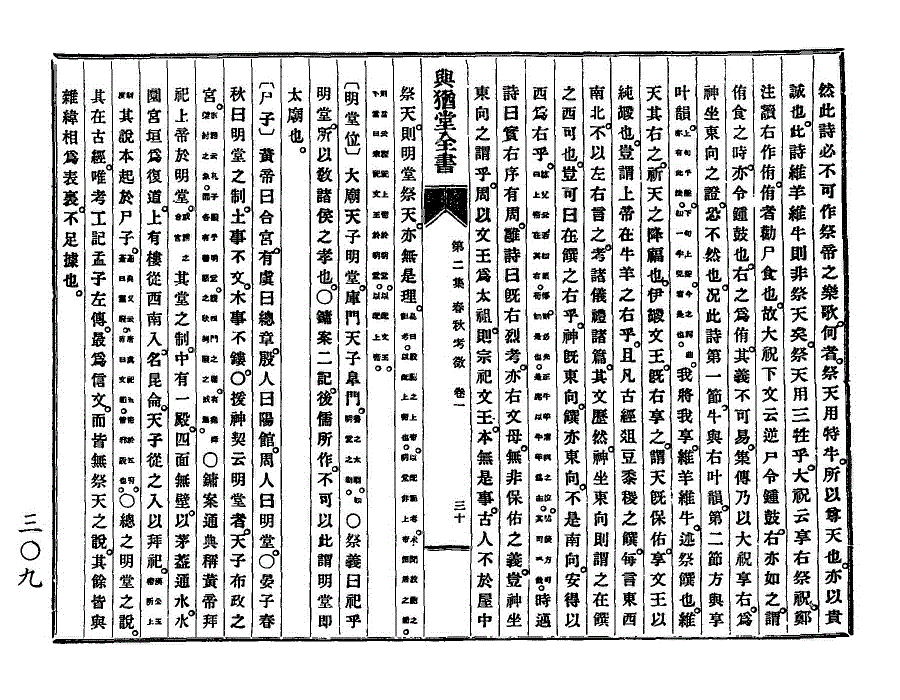 然此诗必不可作祭帝之乐歌。何者。祭天用特牛。所以尊天也。亦以贵诚也。此诗维羊维牛则非祭天矣。祭天用三牲乎。大祝云享右祭祝。郑注读右作侑。侑者劝尸食也。故大祝下文云逆尸令钟鼓。右亦如之。谓侑食之时。亦令钟鼓也。右之为侑。其义不可易。集传乃以大祝享右。为神坐东向之證。恐不然也。况此诗第一节。牛与右叶韵。第二节方与享叶韵。(上句平声。下句上声。今之词曲。亦有此法。如一半儿者是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述祭馔也。维天其右之。祈天之降福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谓天既保佑。享文王以纯嘏也。岂谓上帝在牛羊之右乎。且凡古经俎豆黍稷之馔。每言东西南北。不以左右言之。考诸仪礼诸篇。其文历然。神坐东向则谓之在馔之西可也。岂可曰在馔之右乎。神既东向。馔亦东向。不是南向。安得以西为右乎。(纮父云若如集传。则必先正牛羊南向之位。然后方可曰上帝在其右。苟如是也。是席以牛羊为主。其可乎哉。)时迈诗曰实右序有周。雍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无非保佑之义。岂神坐东向之谓乎。周以文王为太祖。则宗祀文王。本无是事。古人不于屋中祭天。则明堂祭天。亦无是理。(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未闻殷荐之祖考。以配上帝也。明堂非上帝恒居之屋。则当云禋祀上帝于明堂。以配文王。不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然此诗必不可作祭帝之乐歌。何者。祭天用特牛。所以尊天也。亦以贵诚也。此诗维羊维牛则非祭天矣。祭天用三牲乎。大祝云享右祭祝。郑注读右作侑。侑者劝尸食也。故大祝下文云逆尸令钟鼓。右亦如之。谓侑食之时。亦令钟鼓也。右之为侑。其义不可易。集传乃以大祝享右。为神坐东向之證。恐不然也。况此诗第一节。牛与右叶韵。第二节方与享叶韵。(上句平声。下句上声。今之词曲。亦有此法。如一半儿者是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述祭馔也。维天其右之。祈天之降福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谓天既保佑。享文王以纯嘏也。岂谓上帝在牛羊之右乎。且凡古经俎豆黍稷之馔。每言东西南北。不以左右言之。考诸仪礼诸篇。其文历然。神坐东向则谓之在馔之西可也。岂可曰在馔之右乎。神既东向。馔亦东向。不是南向。安得以西为右乎。(纮父云若如集传。则必先正牛羊南向之位。然后方可曰上帝在其右。苟如是也。是席以牛羊为主。其可乎哉。)时迈诗曰实右序有周。雍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无非保佑之义。岂神坐东向之谓乎。周以文王为太祖。则宗祀文王。本无是事。古人不于屋中祭天。则明堂祭天。亦无是理。(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未闻殷荐之祖考。以配上帝也。明堂非上帝恒居之屋。则当云禋祀上帝于明堂。以配文王。不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位〕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鲁之太庙。如明堂之制。)〇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〇镛案二记。后儒所作。不可以此谓明堂即太庙也。
〔尸子〕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〇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镂。〇援神契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家语云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之牖。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〇镛案通典称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谓之合宫)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汉公玉带所上制度)其说本起于尸子。(通典又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苍曰灵府。赤曰文祖。皆邪说也。)〇总之明堂之说。其在古经。唯考工记孟子左传。最为信文。而皆无祭天之说。其馀皆与杂纬相为表里。不足据也。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0H 页
 〔月令〕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〇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周谓之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庙。飨射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虽各异名而其实一也。〇镛案王莽仰看斗杓。旋其坐席。其术盖本于此。为人君者。南面而治。天地之大义也。玄堂太庙。北面以御冬。得无寒乎。然且左个右个之制。必斜割四维。各占其半。然后其义均正。若正割其半。则横于东者竖于南。便于西则碍于北。将何以正体出治乎。法洛书龟文。法洪范九畴。象八卦象五行。虽天地奇妙之理。无不法象。其于用不便而居不安何哉。况以九区一堂。奉昊天上帝。奉五方天帝。奉五方人帝。奉五方神佐。因之为宗庙。兼之为大寝。(天子之正堂)为泽宫为辟雍为灵台为太学。天下有此法乎。悲田乞儿。得一毙袄。跃然以喜曰善哉吾服也。衣之为衣。垂之为裳。藉之为褥。覆之为衾。曲袂则为枕。括袪则为橐。明堂之制。无亦类是。驺衍吕不韦之学。其坏灭王章。感乱人心。无往而不如是矣。(汲冢周书。亦有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诸语。)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〇赵云泰山下明堂。奉周天子朝诸侯之处也。(疏云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诸侯之处。)〇镛案周天子立其宗庙于泰山。有是理乎。齐之明堂。周之行宫。天子无外。凡出治之所。在内在外。皆称明堂。(春秋释例云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大庙与明堂一体也。)
〔月令〕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〇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周谓之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庙。飨射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虽各异名而其实一也。〇镛案王莽仰看斗杓。旋其坐席。其术盖本于此。为人君者。南面而治。天地之大义也。玄堂太庙。北面以御冬。得无寒乎。然且左个右个之制。必斜割四维。各占其半。然后其义均正。若正割其半。则横于东者竖于南。便于西则碍于北。将何以正体出治乎。法洛书龟文。法洪范九畴。象八卦象五行。虽天地奇妙之理。无不法象。其于用不便而居不安何哉。况以九区一堂。奉昊天上帝。奉五方天帝。奉五方人帝。奉五方神佐。因之为宗庙。兼之为大寝。(天子之正堂)为泽宫为辟雍为灵台为太学。天下有此法乎。悲田乞儿。得一毙袄。跃然以喜曰善哉吾服也。衣之为衣。垂之为裳。藉之为褥。覆之为衾。曲袂则为枕。括袪则为橐。明堂之制。无亦类是。驺衍吕不韦之学。其坏灭王章。感乱人心。无往而不如是矣。(汲冢周书。亦有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诸语。)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〇赵云泰山下明堂。奉周天子朝诸侯之处也。(疏云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诸侯之处。)〇镛案周天子立其宗庙于泰山。有是理乎。齐之明堂。周之行宫。天子无外。凡出治之所。在内在外。皆称明堂。(春秋释例云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大庙与明堂一体也。)〔左传〕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云明堂。祖庙也。)〇孔曰郑玄以为明堂在国之阳。与祖庙别处。左氏旧说及贾逵、卢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庙与明堂为一。故杜同之。〇镛案杜说非也。
〔大戴礼〕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周时蒿以为柱。名蒿宫。此天子之路寝也。〇镛案戴德之时。或以为宗庙。或以为路寝。其说不一。故记之如此。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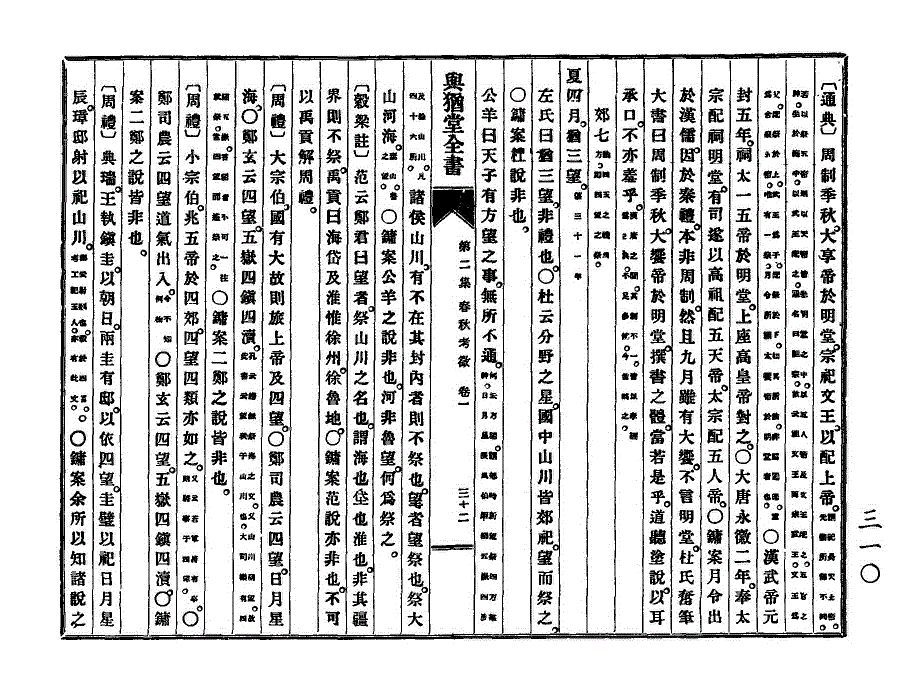 〔通典〕周制季秋。大享帝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谓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释不同。若以祭五帝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为父。配祭于上。武王为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论。非为通理。意为合祭五帝。唯有一祭。月令所谓太(一作大)飨帝于明堂者也。 〇汉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高皇帝对之。〇大唐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〇镛案月令出于汉儒。因于秦礼。本非周制。然且九月虽有大飨。不言明堂。杜氏奋笔大书曰周制季秋。大飨帝于明堂。撰书之体。当若是乎。道听涂说。以耳承口。不亦羞乎。(汉唐之间。其制不一。皆以孝经为古典。不足多辨。今并略之。)
〔通典〕周制季秋。大享帝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谓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释不同。若以祭五帝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为父。配祭于上。武王为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论。非为通理。意为合祭五帝。唯有一祭。月令所谓太(一作大)飨帝于明堂者也。 〇汉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高皇帝对之。〇大唐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〇镛案月令出于汉儒。因于秦礼。本非周制。然且九月虽有大飨。不言明堂。杜氏奋笔大书曰周制季秋。大飨帝于明堂。撰书之体。当若是乎。道听涂说。以耳承口。不亦羞乎。(汉唐之间。其制不一。皆以孝经为古典。不足多辨。今并略之。)郊七(论四玉之礼四方。即四望之祭。)
夏四月。犹三望。(僖三十一年)
左氏曰犹三望。非礼也。〇杜云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〇镛案杜说非也。
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何云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馀山川。凡四(一作三)十六所。 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望者望祭也。祭大山河海。(泰山。鲁之望。)〇镛案公羊之说非也。河非鲁望。何为祭之。
〔谷梁注〕范云郑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谓海也垈(一作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则不祭。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鲁地。〇镛案范说亦非也。不可以禹贡解周礼。
〔周礼〕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〇郑司农云四望。日月星海。〇郑玄云四望。五岳四镇四渎。(孔云礼无祭海之文。又山川称望。故尚书云望秩于山川也。大司乐有四镇五岳。言望者不可一往就祭。当四望而遥祭之。)〇镛案二郑之说皆非也。
〔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又云若军将有事。则将事于四望。)〇郑司农云四望道气出入。(今不知何物)〇郑玄云四望。五岳四镇四渎。〇镛案二郑之说皆非也。
〔周礼〕典瑞。王执镇圭。以朝日。两圭有邸。以依(一作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郑云射剡也。杀于四望。考工记玉人。亦有此文。)〇镛案余所以知诸说之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1H 页
 皆非者。以典瑞玉人之文。明以四望别于日月别于山川也。若四望之中。原有日月星辰四镇四渎。则分其等级。何得若是。然则四望何物也。望者遥祭之名。遥祭山川。可谓之望。遥祭他神。亦可云望。如旅之为礼。只是陈告之义。故旅上帝旅四望旅泰山。皆得言旅也。尧典曰望于山川。尔雅曰梁山。鲁之望。(释山文)左傅(一作传)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哀六年)山川之祭。固亦称望。然周之四望。鲁之三望。必非山川之祭。故典瑞玉人。其文如此。窃尝考之。古者祭典。元有天地四方之名。上祭天神。下祭地示。旁祭四方。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方祀四方者。四望也。觐礼方明之木。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设六玉。盖以方四尺之木。象上下四方之神示。以主盟诅。小可以推大也。故越王句践以会稽封范蠡。而誓之曰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昭云乡。方也。天神地示。四方神主。当征讨之。)其畏四方之神如此。故大宗伯以副辜祭四方。以玉器礼四方。地官舞师以羽舞祭四方。(郑云四方之祭。谓四望也。)祭法云泰坛祭天也。泰折祭地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四方之祭。非四望而何物也。尧典曰望秩于山川。先儒误读此文。遂以四望专属山川之祭。其实望一句。秩于山川又一句。谓四望之祭。其秩视山川也。书注谓五岳之秩视三公。四渎之秩视诸侯。苟如是也。当云望秩于公侯。岂可曰望秩于山川乎。郑以五岳四镇四渎。为四望之神。而其小宗伯之注。乃以四望。分兆四郊。此又不通之论也。五岳兆于四郊。则中岳之神。客无所之。何况四镇者。东方之四山也。霍山医无闾。在于东北。(在冀州幽州)沂山会稽。在于东南。(在青州扬州)四方之山。了无影响。而强分四郊可乎。四渎者。江淮河汉也。江淮河汉。皆源西而流东。不可摘其一二。偏属东西。若云河于北郊。江于南郊。则淮汉二神。客无所之。左右揆度。岳渎之非四望。亦已审矣。四望者。四方之祭。非他物也。公美(一作羊)氏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者四望也。鲁人之为三望者。天子全举四方。诸侯阙其一方。如四时之祭。天子四举。诸侯三祭。(见王制)四霤之制。天子四阿。诸侯三流也。(见礼注)若然东侯不祭西方。南侯不祭北方。西北
皆非者。以典瑞玉人之文。明以四望别于日月别于山川也。若四望之中。原有日月星辰四镇四渎。则分其等级。何得若是。然则四望何物也。望者遥祭之名。遥祭山川。可谓之望。遥祭他神。亦可云望。如旅之为礼。只是陈告之义。故旅上帝旅四望旅泰山。皆得言旅也。尧典曰望于山川。尔雅曰梁山。鲁之望。(释山文)左傅(一作传)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哀六年)山川之祭。固亦称望。然周之四望。鲁之三望。必非山川之祭。故典瑞玉人。其文如此。窃尝考之。古者祭典。元有天地四方之名。上祭天神。下祭地示。旁祭四方。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方祀四方者。四望也。觐礼方明之木。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设六玉。盖以方四尺之木。象上下四方之神示。以主盟诅。小可以推大也。故越王句践以会稽封范蠡。而誓之曰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昭云乡。方也。天神地示。四方神主。当征讨之。)其畏四方之神如此。故大宗伯以副辜祭四方。以玉器礼四方。地官舞师以羽舞祭四方。(郑云四方之祭。谓四望也。)祭法云泰坛祭天也。泰折祭地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四方之祭。非四望而何物也。尧典曰望秩于山川。先儒误读此文。遂以四望专属山川之祭。其实望一句。秩于山川又一句。谓四望之祭。其秩视山川也。书注谓五岳之秩视三公。四渎之秩视诸侯。苟如是也。当云望秩于公侯。岂可曰望秩于山川乎。郑以五岳四镇四渎。为四望之神。而其小宗伯之注。乃以四望。分兆四郊。此又不通之论也。五岳兆于四郊。则中岳之神。客无所之。何况四镇者。东方之四山也。霍山医无闾。在于东北。(在冀州幽州)沂山会稽。在于东南。(在青州扬州)四方之山。了无影响。而强分四郊可乎。四渎者。江淮河汉也。江淮河汉。皆源西而流东。不可摘其一二。偏属东西。若云河于北郊。江于南郊。则淮汉二神。客无所之。左右揆度。岳渎之非四望。亦已审矣。四望者。四方之祭。非他物也。公美(一作羊)氏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者四望也。鲁人之为三望者。天子全举四方。诸侯阙其一方。如四时之祭。天子四举。诸侯三祭。(见王制)四霤之制。天子四阿。诸侯三流也。(见礼注)若然东侯不祭西方。南侯不祭北方。西北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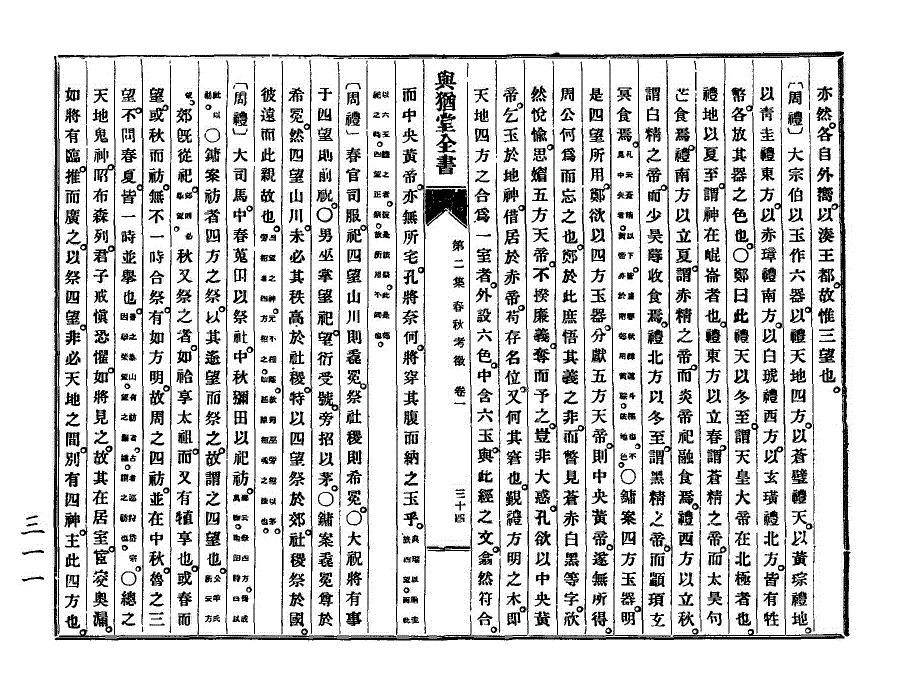 亦然。各自外向。以凑王都。故惟三望也。
亦然。各自外向。以凑王都。故惟三望也。〔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也。〇郑曰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崙者也。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而炎帝祀(一作祝)融食焉。礼西方以立秋。谓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以冬至。谓黑精之帝。而颛顼玄冥食焉。(孔云苍精以下。皆据春秋纬运斗枢也。不见中央者。黄帝亦于南郊用黄琮。依地色。)〇镛案四方玉器。明是四望所用。郑欲以四方玉器。分献五方天帝。则中央黄帝。遂无所得。周公何为而忘之也。郑于此庶悟其义之非。而瞥见苍赤白黑等字。欣然悦愉(愉悦)。思媚五方天帝。不揆廉义。夺而予之。岂非大惑。孔欲以中央黄帝。乞玉于地神。借居于赤帝。苟存名位。又何其窘也。觐礼方明之木。即天地四方之合为一室者。外设六色。中含六玉。与此经之文。翕然符合。而中央黄帝。亦无所宅。孔将奈何。将穿其腹而纳之玉乎。(典瑞以两圭旅四望。而此以六玉礼之者。彼是旅祭。此是郊祀之时。四望正祭。故所用不同也。)
〔周礼〕春官司服。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则希冕。〇大祝将有事于四望则前祝。〇男巫掌望祀。望衍受号。旁招以茅。〇镛案毳冕尊于希冕。然四望山川。未必其秩高于社稷。特以四望祭于郊。社稷祭于国。彼远而此亲故也。(四望之神。元不相离。故男巫旁招以茅。旁招者四方招之。如屈原招魂之法也。)
〔周礼〕大司马。中春蒐田以祭社。中秋猕(一作狝)田以祀祊。(郑云祭四方。报成万物。甫田诗曰以社以祊。)〇镛案祊者四方之祭。以其遥望而祭之。故谓之四望也。(公羊氏所云方望。)郊既从祀。(郊则必举望。)秋又祭之者。如祫享太祖。而又有犆享也。或春而望。或秋而祊。无不一时合祭。有如方明。故周之四祊。并在中秋。鲁之三望。不问春夏。皆一时并举也。(鲁之泰山有祊者。古者巡狩岱宗。因举柴望。望之旧墟。谓之祊也。)〇总之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君子戒慎恐惧。如将见之。故其在居室。宦㝔奥漏。如将有临。推而广之。以祭四望。非必天地之间。别有四神。主此四方也。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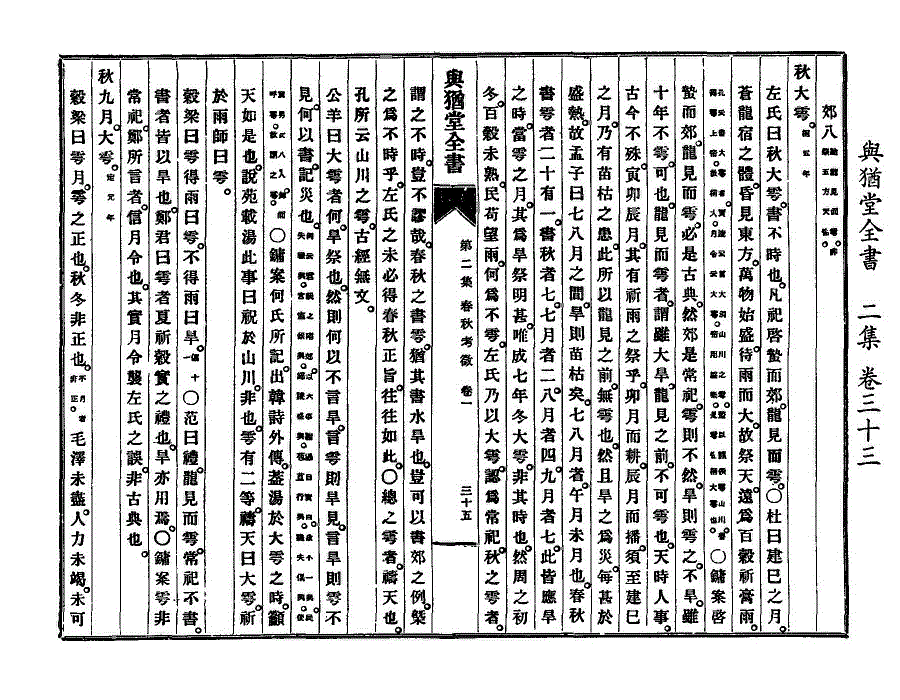 郊八(论龙见而雩。非祭五方天帝。)
郊八(论龙见而雩。非祭五方天帝。)秋大雩。(桓五年)
左氏曰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〇杜曰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孔云书大雩者。贾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盖以诸侯雩山川。鲁得雩上帝。故称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乐。是雩帝称大雩也。)〇镛案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必是古典。然郊是常祀。雩则不然。旱则雩之。不旱。虽十年不雩。可也。龙见而雩者。谓虽大旱。龙见之前。不可雩也。天时人事。古今不殊。寅卯辰月。其有祈雨之祭乎。卯月而耕。辰月而播。须至建巳之月。乃有苗枯之患。此所以龙见之前。无雩也。然且旱之为灾。每甚于盛热。故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枯矣。七八月者。午月未月也。春秋书雩者二十有一。书秋者七。七月者二。八月者四。九月者七。此皆应旱之时。当雩之月。其为旱祭明甚。唯成七年冬大雩。非其时也。然周之初冬。百谷未熟。民苟望雨。何为不雩。左氏乃以大雩。认为常祀。秋之雩者。谓之不时。岂不谬哉。春秋之书雩。犹其书水旱也。岂可以书郊之例。槩之为不时乎。左氏之未必得春秋正旨。往往如此。〇总之雩者。祷天也。孔所云山川之雩。古经无文。
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何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目(一作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使童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 〇镛案何氏所记。出韩诗外传。盖汤于大雩之时。吁天如是也。说苑载汤此事曰祝于山川。非也。雩有二等。祷天曰大雩。祈于雨师曰雩。
谷梁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僖十一)〇范曰礼。龙见而雩。常祀不书。书者皆以旱也。郑君曰雩者夏祈谷实之礼也。旱亦用焉。〇镛案雩非常祀。郑所言者。信月令也。其实月令袭左氏之误。非古典也。
秋九月。大雩。(定元年)
谷梁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冬非正也。(不月者非正。)毛泽未尽。人力未竭。未可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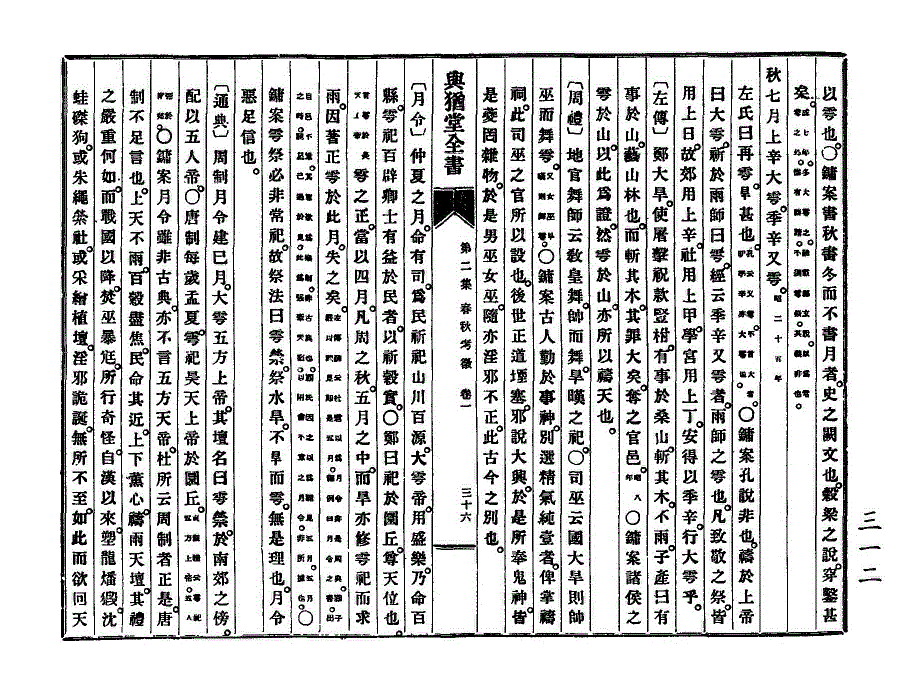 以雩也。〇镛案书秋书冬而不书月者。史之阙文也。谷梁之说。穿凿甚矣。(成七年。冬大雩之。疏载郑玄说。以为常雩之外。惟有祷请。不须雩祭。其义非也。)
以雩也。〇镛案书秋书冬而不书月者。史之阙文也。谷梁之说。穿凿甚矣。(成七年。冬大雩之。疏载郑玄说。以为常雩之外。惟有祷请。不须雩祭。其义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二十五年)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孔云又雩。不言大者。明季辛亦大雩也。)〇镛案孔说非也。祷于上帝曰大雩。祈于雨师曰雩。经云季辛又雩者。雨师之雩也。凡致敬之祭。皆用上日。故郊用上辛。社用上甲。学宫用上丁。安得以季辛。行大雩乎。
〔左传〕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昭八年)〇镛案诸侯之雩于山。以此为證。然雩于山。亦所以祷天也。
〔周礼〕地官舞师云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祀。〇司巫云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又女巫旱暵则舞雩。)镛案古人勤于事神。别选精气纯壹者。俾掌祷祠。此司巫之官所以设也。后世正道堙塞。邪说大兴。于是所奉鬼神。皆是夔罔杂物。于是男巫女巫。随亦淫邪不正。此古今之别也。
〔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〇郑曰祀于圜丘。尊天位也。(言雩于昊天上帝)雩之正。当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于此月。失之矣。(左传疏云杜君以为月令非是周典。颍子严以龙见即是五月。释例曰月令之书。出自吕不韦。其意欲为秦制。非古典也。颍氏因之以为龙见五月。五月之时。龙星已过于见。此为强牵天宿。以附会不韦之月令。非所据也。)〇镛案雩祭必非常祀。故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不旱而雩。无是理也。月令恶足信也。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坛名曰雩禜。于南郊之傍。配以五人帝。〇唐制每岁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贞观礼云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于南郊。)〇镛案月令虽非古典。亦不言五方天帝。杜所云周制者正是。唐制不足言也。上天不雨。百谷尽焦。民命其近。上下薰心。祷雨天坛。其礼之严重何如。而战国以降。焚巫暴尪。所行奇怪。自汉以来。塑龙燔猳。沈蛙磔狗。或朱绳萦社。或采缯植坛。淫邪诡诞。无所不至。如此而欲回天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3H 页
 怒而救民命。难矣。〇又按唐制祈雨。先祭岳渎。次祭山川。次祈社稷。次祈宗庙。每以七日为限。一祈不雨。周而复始。今吾东之法。盖遵唐制。噫稽之古典。其有雩于社稷。雩于宗庙者乎。雩于山川。亦无正文。
怒而救民命。难矣。〇又按唐制祈雨。先祭岳渎。次祭山川。次祈社稷。次祈宗庙。每以七日为限。一祈不雨。周而复始。今吾东之法。盖遵唐制。噫稽之古典。其有雩于社稷。雩于宗庙者乎。雩于山川。亦无正文。郊九(论司中司命。非文昌二星。)
〔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〇郑司农曰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郑玄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疏云春秋纬云月离于箕。风扬沙。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〇镛案纬家仰观列星。森罗满天。便欲以此辟一朝廷。于是推一星以为上帝。(耀魄宝)推五星以为五帝。(太微垣。)三公六卿。文武百官。无所不备。于是诸凡经文之言天神者。悉以星当之。此非细事。噫吾人者。万物之灵。彼穹天厚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无一而非吾人之物。天吾屋也。地吾食也。日月星辰。吾所明也。山川草木。吾所养也。彼皆有气有质。无情无灵。岂吾人所能事哉。惟其百神奔属。受命帝庭。或司日月星辰。或司土谷山川。圣人列于祀典。以广昭事之义。注疏之家。每指有形之物。奉之为神。恶乎可哉。司中者。不知何神。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成十三)尧舜相传之言曰允执其中。秋官司刺。以三法断民中。(小司寇岁终则登中于天府。)其字义可知也。天道福善祸淫。司中之神。容亦有之。楚辞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古注谓之主人生死。大司命云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王逸云九州之民众多。其寿夭皆自施行所致。天诛加之。不在于我也。)又曰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王逸云言人受命而生。)少司命云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王逸云艾。长也。言司命持长剑。以诛凶恶。拥护长少。使各得其命也。〇或云艾。少也。)古人原谓天神之中。有司中司命。故祭之以槱燎。彼所谓文昌二星。何与于是。(史记扁鹊传云扁鹊视赵简子之病曰。病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〇江淹遂古篇云太一司命鬼之元兮。)〇又按风师雨师。亦非箕毕。夫诸星隐德。各有招摄。而其性气所主。人皆茫昧。惟箕毕二星。偶见称道。郑玄遂以二星。封为二师。其实不稽之言也。天之百神。本无形质。安得以煜煜之光。指之为神哉。
〔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节)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〇镛案
第二集经集第三十三卷○春秋考徵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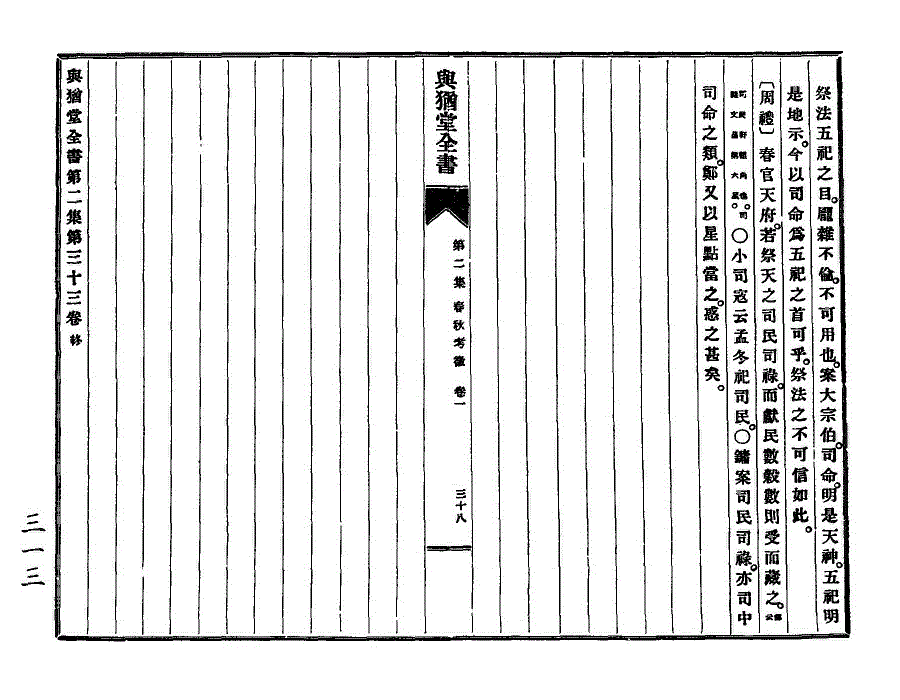 祭法五祀之目。庞杂不伦。不可用也。案大宗伯。司命。明是天神。五祀明是地示。今以司命为五祀之首可乎。祭法之不可信如此。
祭法五祀之目。庞杂不伦。不可用也。案大宗伯。司命。明是天神。五祀明是地示。今以司命为五祀之首可乎。祭法之不可信如此。〔周礼〕春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郑云司民轩辕角也。司禄文昌第六星。)〇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〇镛案司民司禄。亦司中司命之类。郑又以星点当之。惑之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