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x 页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书类
书类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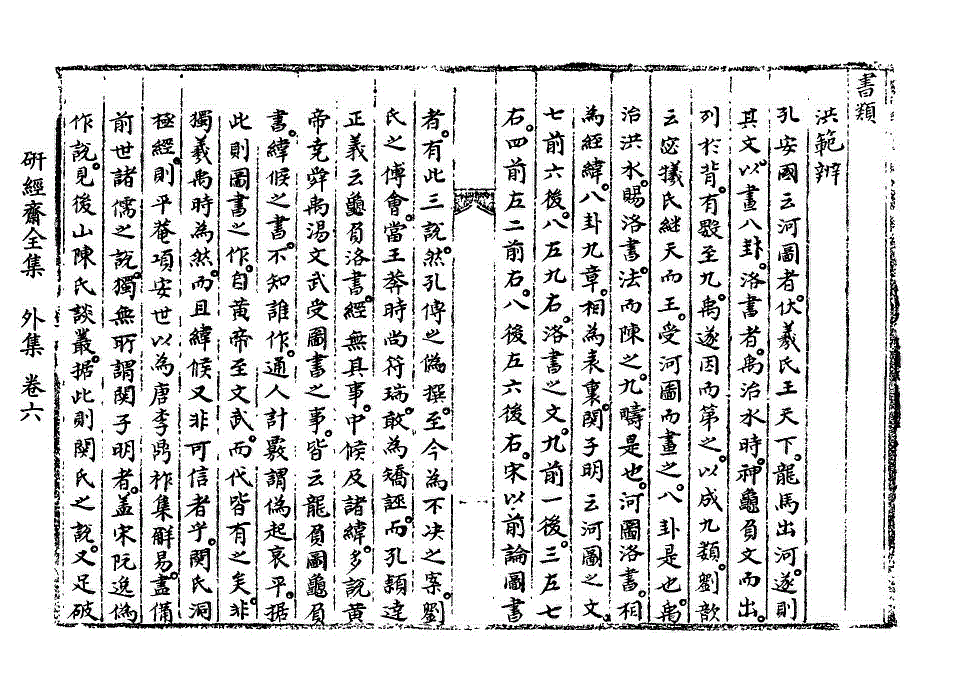 洪范辨
洪范辨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刘歆云宓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宋以前论图书者。有此三说。然孔传之伪撰。至今为不决之案。刘氏之傅会。当王莽时尚符瑞。敢为矫诬。而孔颖达正义云龟负洛书。经无其事。中候及诸纬。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图书之事。皆云龙负图龟负书。纬候之书。不知谁作。通人计覈谓伪起哀平。据此则图书之作。自黄帝至文武。而代皆有之矣。非独羲禹时为然。而且纬候又非可信者乎。关氏洞极经。则平庵项安世以为唐李鼎祚集解易。尽备前世诸儒之说。独无所谓关子明者。盖宋阮逸伪作说。见后山陈氏谈丛。据此则关氏之说。又足破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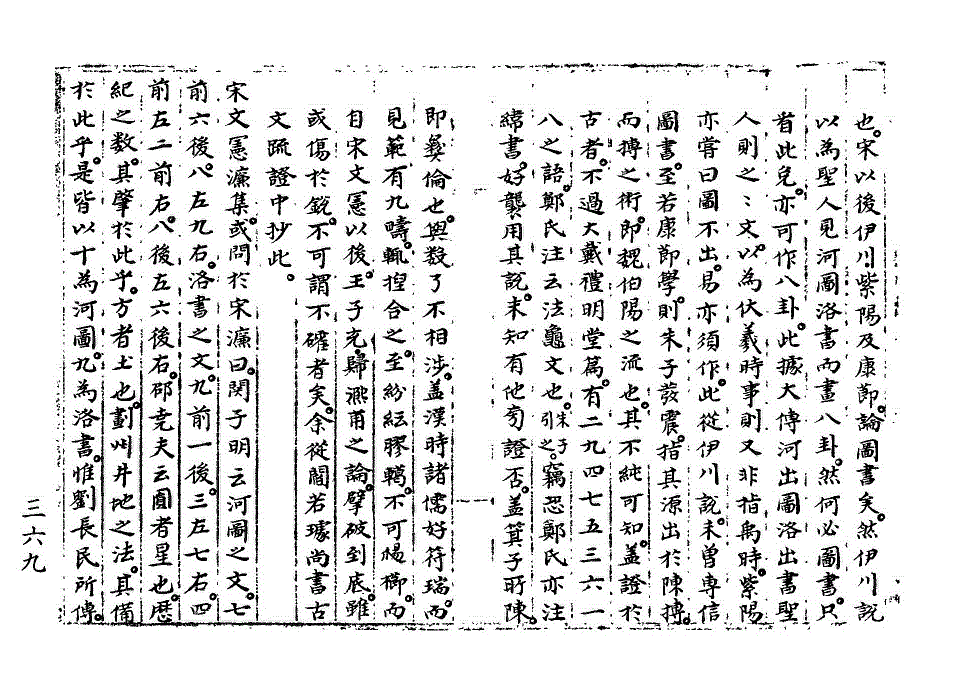 也。宋以后伊川,紫阳及康节。论图书矣。然伊川说以为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免。亦可作八卦。此据大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文。以为伏羲时事则又非指禹时。紫阳亦尝曰图不出。易亦须作。此从伊川说。未曾专信图书。至若康节学。则朱子发震。指其源出于陈抟。而抟之𧗱。即魏伯阳之流也。其不纯可知。盖證于古者。不过大戴礼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郑氏注云法龟文也。(朱子引之。)窃恐郑氏亦注纬书。好袭用其说。未知有他旁證否。盖箕子所陈。即彝伦也。与数了不相涉。盖汉时诸儒好符瑞。而见范有九畴。辄捏合之。至纷纭胶轕。不可㼒(一作瓣)栉。而自宋文宪以后。王子充,归熙甫之论。擘破到底。虽或伤于锐。不可谓不礭者矣。余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證中抄此。
也。宋以后伊川,紫阳及康节。论图书矣。然伊川说以为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免。亦可作八卦。此据大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文。以为伏羲时事则又非指禹时。紫阳亦尝曰图不出。易亦须作。此从伊川说。未曾专信图书。至若康节学。则朱子发震。指其源出于陈抟。而抟之𧗱。即魏伯阳之流也。其不纯可知。盖證于古者。不过大戴礼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郑氏注云法龟文也。(朱子引之。)窃恐郑氏亦注纬书。好袭用其说。未知有他旁證否。盖箕子所陈。即彝伦也。与数了不相涉。盖汉时诸儒好符瑞。而见范有九畴。辄捏合之。至纷纭胶轕。不可㼒(一作瓣)栉。而自宋文宪以后。王子充,归熙甫之论。擘破到底。虽或伤于锐。不可谓不礭者矣。余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證中抄此。宋文宪濂集。或问于宋濂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尧夫云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划州井地之法。其备于此乎。是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惟刘长民所传。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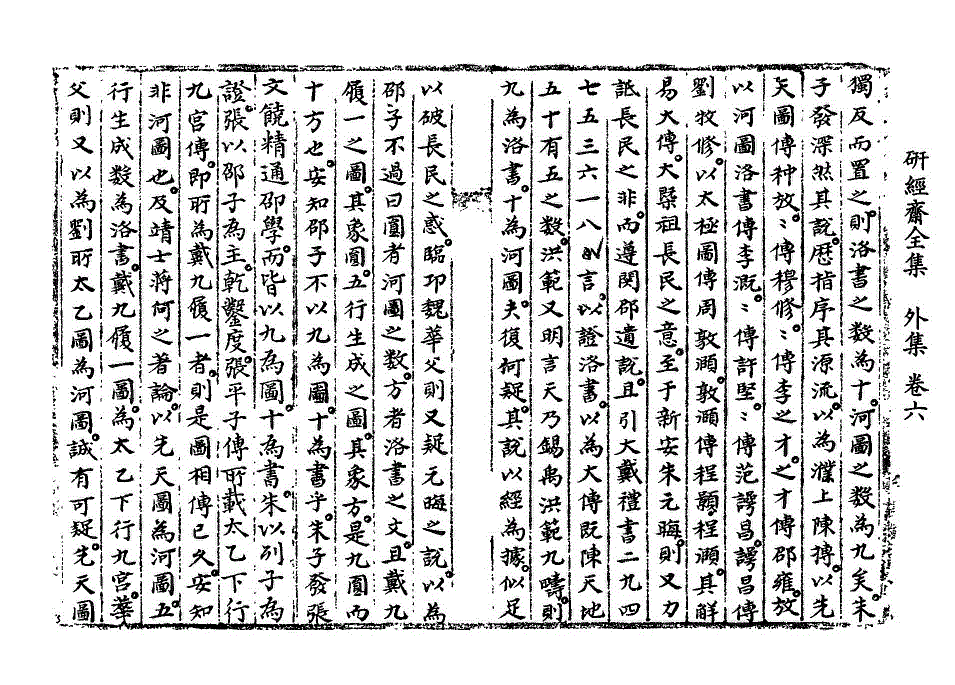 独反而置之。则洛书之数为十。河图之数为九矣。朱子发深然其说。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其解易大传。大槩祖长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则又力诋长民之非。而遵关邵遗说。且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言。以證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其说以经为据。似足以破长民之惑。临邛魏华父则又疑元晦之说。以为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證。张以邵子为主。乾凿度。张平子传所载太乙下行九宫传。即所为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及靖士蒋何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华父则又以为刘所太乙图为河图。诚有可疑。先天图
独反而置之。则洛书之数为十。河图之数为九矣。朱子发深然其说。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其解易大传。大槩祖长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则又力诋长民之非。而遵关邵遗说。且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言。以證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其说以经为据。似足以破长民之惑。临邛魏华父则又疑元晦之说。以为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證。张以邵子为主。乾凿度。张平子传所载太乙下行九宫传。即所为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及靖士蒋何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华父则又以为刘所太乙图为河图。诚有可疑。先天图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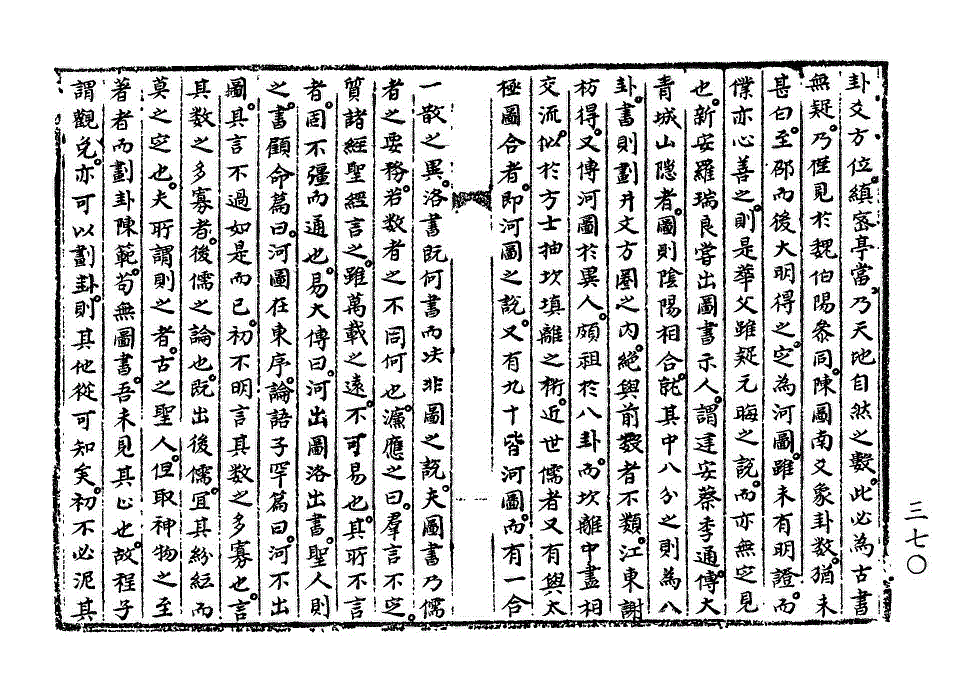 卦爻方位。缜密亭当。乃天地自然之数。此必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而后大明得之。定为河图。虽未有明證。而仆亦心善之。则是华父虽疑元晦之说。而亦无定见也。新安罗瑞良尝出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大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划井文方圈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尽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𧗱。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何书而决非图之说。夫图书乃儒者之要务。若数者之不同何也。濂应之曰。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彊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言其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划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正也。故程子谓观免。亦可以划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
卦爻方位。缜密亭当。乃天地自然之数。此必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而后大明得之。定为河图。虽未有明證。而仆亦心善之。则是华父虽疑元晦之说。而亦无定见也。新安罗瑞良尝出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大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划井文方圈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尽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𧗱。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何书而决非图之说。夫图书乃儒者之要务。若数者之不同何也。濂应之曰。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彊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言其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划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正也。故程子谓观免。亦可以划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1H 页
 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惟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盖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果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则善矣。若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所谓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者。将果足治乎。濂曰。龟山杨中立不云乎。圣人但云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龙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此盖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启司马君实及欧阳永叔之辨。而并大传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杨雄覈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长民亦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划八卦。然则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欤。濂曰。先儒固当有疑于此。揆之于经。其言皆无以验。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畴。相为表里。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
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惟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盖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果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则善矣。若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所谓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者。将果足治乎。濂曰。龟山杨中立不云乎。圣人但云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龙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此盖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启司马君实及欧阳永叔之辨。而并大传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杨雄覈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长民亦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划八卦。然则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欤。濂曰。先儒固当有疑于此。揆之于经。其言皆无以验。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畴。相为表里。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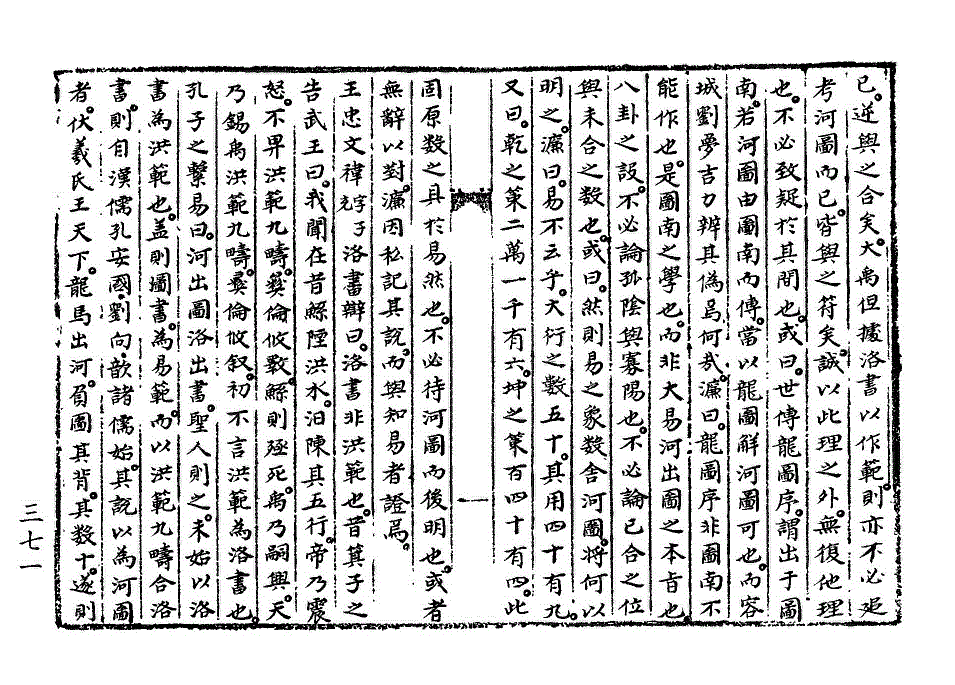 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皆与之符矣。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也。不必致疑于其间也。或曰。世传龙图序。谓出于图南。若河图由图南而传。当以龙图解河图可也。而容城刘梦吉力辨其伪焉何哉。濂曰。龙图序非图南不能作也。是图南之学也。而非大易河出图之本旨也。八卦之设。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也。或曰。然则易之象数舍河图。将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万一千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原数之具于易然也。不必待河图而后明也。或者无辞以对。濂因私记其说。而与知易者證焉。
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皆与之符矣。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也。不必致疑于其间也。或曰。世传龙图序。谓出于图南。若河图由图南而传。当以龙图解河图可也。而容城刘梦吉力辨其伪焉何哉。濂曰。龙图序非图南不能作也。是图南之学也。而非大易河出图之本旨也。八卦之设。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也。或曰。然则易之象数舍河图。将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万一千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原数之具于易然也。不必待河图而后明也。或者无辞以对。濂因私记其说。而与知易者證焉。王忠文祎(字子充)洛书辩曰。洛书非洪范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不言洪范为洛书也。孔子之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始以洛书为洪范也。盖则图书。为易范。而以洪范九畴合洛书。则自汉儒孔安国,刘向,歆诸儒始。其说以为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负图其背。其数十。遂则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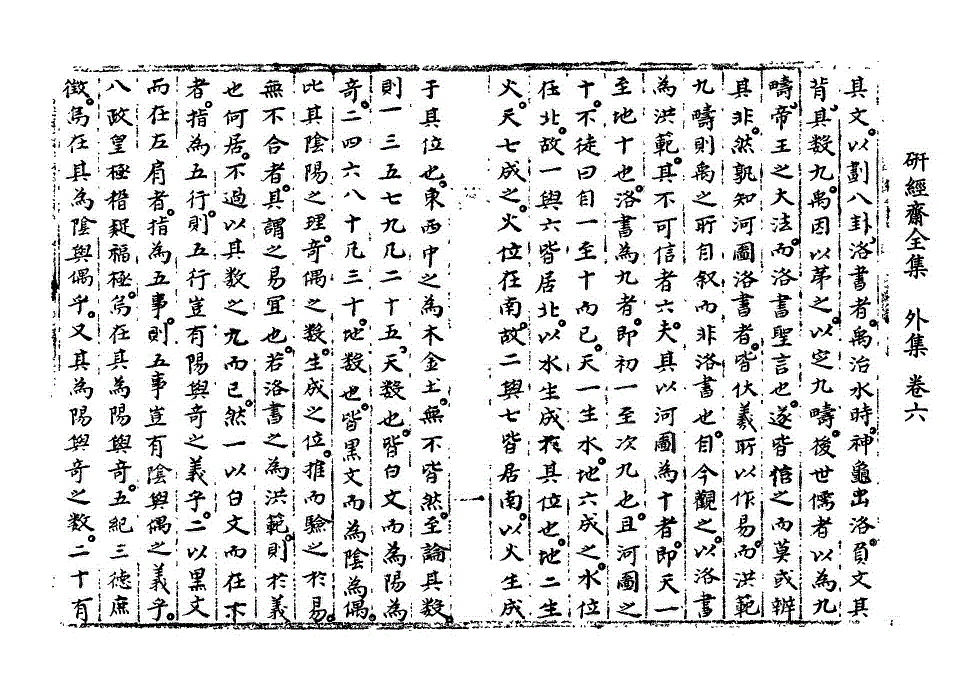 其文。以划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出洛。负文其背。其数九。禹因以第之。以定九畴。后世儒者以为九畴。帝王之大法。而洛书圣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图洛书者。皆伏羲所以作易。而洪范九畴则禹之所自叙而非洛书也。自今观之。以洛书为洪范。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图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书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图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与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与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东西中之为木金土。无不皆然。至论其数。则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数也。皆白文而为阳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数也。皆黑文而为阴为偶。比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而验之于易。无不合者。其谓之易宜也。若洛书之为洪范。则于义也何居。不过以其数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为五行。则五行岂有阳与奇之义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为五事。则五事岂有阴与偶之义乎。八政皇极稽疑福极。乌在其为阳与奇。五纪三德庶徵。乌在其为阴与偶乎。又其为阳与奇之数。二十有
其文。以划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出洛。负文其背。其数九。禹因以第之。以定九畴。后世儒者以为九畴。帝王之大法。而洛书圣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图洛书者。皆伏羲所以作易。而洪范九畴则禹之所自叙而非洛书也。自今观之。以洛书为洪范。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图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书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图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与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与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东西中之为木金土。无不皆然。至论其数。则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数也。皆白文而为阳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数也。皆黑文而为阴为偶。比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而验之于易。无不合者。其谓之易宜也。若洛书之为洪范。则于义也何居。不过以其数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为五行。则五行岂有阳与奇之义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为五事。则五事岂有阴与偶之义乎。八政皇极稽疑福极。乌在其为阳与奇。五纪三德庶徵。乌在其为阴与偶乎。又其为阳与奇之数。二十有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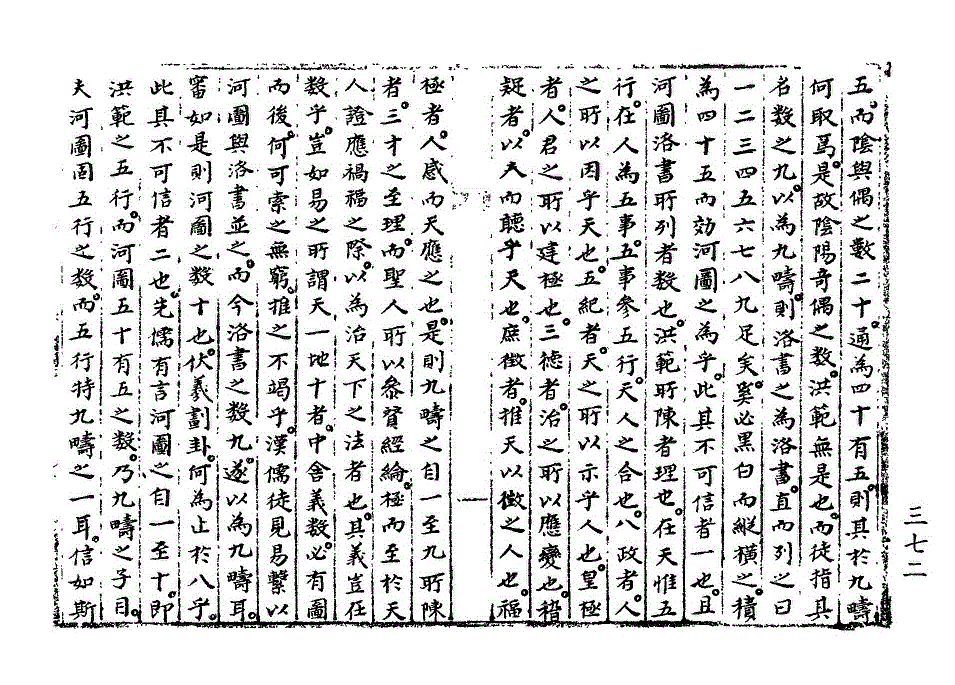 五。而阴与偶之数二十。通为四十有五。则其于九畴何取焉。是故阴阳奇偶之数。洪范无是也。而徒指其名数之九。以为九畴。则洛书之为洛书。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纵横之。积为四十五而效河图之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图洛书所列者数也。洪范所陈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参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极者。人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乎天也。庶徵者。推天以徵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之也。是则九畴之自一至九所陈者。三才之至理。而圣人所以参赞经纶。极而至于天人證应祸福之际。以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义岂在数乎。岂如易之所谓天一地十者。中舍义数。必有图而后。何可索之无穷。推之不竭乎。汉儒徒见易系以河图与洛书并之。而今洛书之数九。遂以为九畴耳。审如是则河图之数十也。伏羲划卦。何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图之自一至十。即洪范之五行。而河图五十有五之数。乃九畴之子目。夫河图固五行之数。而五行特九畴之一耳。信如斯
五。而阴与偶之数二十。通为四十有五。则其于九畴何取焉。是故阴阳奇偶之数。洪范无是也。而徒指其名数之九。以为九畴。则洛书之为洛书。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纵横之。积为四十五而效河图之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图洛书所列者数也。洪范所陈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参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极者。人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乎天也。庶徵者。推天以徵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之也。是则九畴之自一至九所陈者。三才之至理。而圣人所以参赞经纶。极而至于天人證应祸福之际。以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义岂在数乎。岂如易之所谓天一地十者。中舍义数。必有图而后。何可索之无穷。推之不竭乎。汉儒徒见易系以河图与洛书并之。而今洛书之数九。遂以为九畴耳。审如是则河图之数十也。伏羲划卦。何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图之自一至十。即洪范之五行。而河图五十有五之数。乃九畴之子目。夫河图固五行之数。而五行特九畴之一耳。信如斯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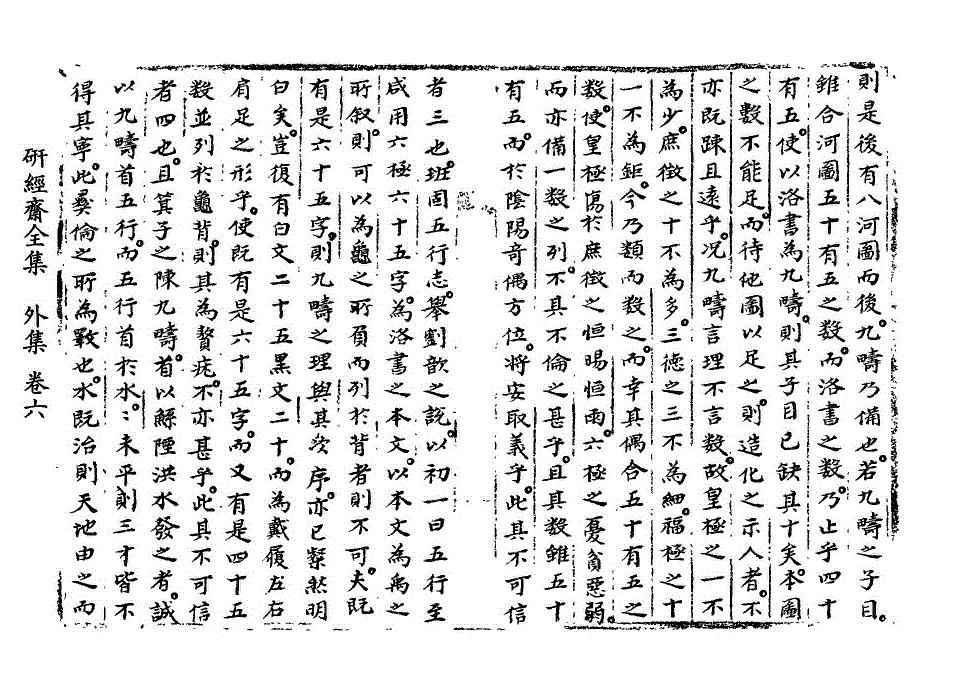 则是后有八河图而后。九畴乃备也。若九畴之子目。虽合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洛书之数。乃止乎四十有五。使以洛书为九畴。则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图之数不能足。而待他图以足之。则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远乎。况九畴言理不言数。故皇极之一不为少。庶徵之十不为多。三德之三不为细。福极之十一不为钜。今乃类而数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数。使皇极伤于庶徵之恒旸恒雨。六极之忧贫恶弱。而亦备一数之列。不其不伦之甚乎。且其数虽五十有五。而于阴阳奇偶方位。将安取义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举刘歆之说。以初一曰五行至咸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以本文为禹之所叙。则可以为龟之所负而列于背者则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则九畴之理与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岂复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数并列于龟背。则其为赘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陈九畴。首以鲧堙洪水发之者。诚以九畴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则三才皆不得其宁。此彝伦之所为斁也。水既治则天地由之而
则是后有八河图而后。九畴乃备也。若九畴之子目。虽合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洛书之数。乃止乎四十有五。使以洛书为九畴。则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图之数不能足。而待他图以足之。则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远乎。况九畴言理不言数。故皇极之一不为少。庶徵之十不为多。三德之三不为细。福极之十一不为钜。今乃类而数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数。使皇极伤于庶徵之恒旸恒雨。六极之忧贫恶弱。而亦备一数之列。不其不伦之甚乎。且其数虽五十有五。而于阴阳奇偶方位。将安取义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举刘歆之说。以初一曰五行至咸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以本文为禹之所叙。则可以为龟之所负而列于背者则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则九畴之理与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岂复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数并列于龟背。则其为赘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陈九畴。首以鲧堙洪水发之者。诚以九畴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则三才皆不得其宁。此彝伦之所为斁也。水既治则天地由之而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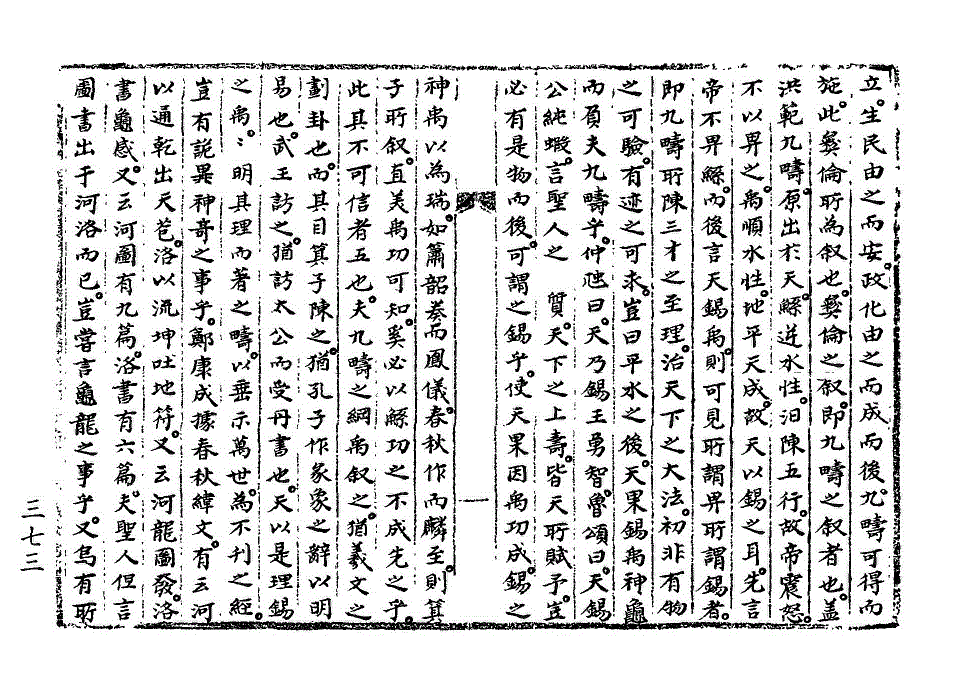 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后。九畴可得而施。此彝伦所为叙也。彝伦之叙。即九畴之叙者也。盖洪范九畴。原出于天。鲧逆水性。汩陈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顺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锡之耳。先言帝不畀鲧。而后言天锡禹。则可见所谓畀所谓锡者。即九畴所陈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验。有迹之可求。岂曰平水之后。天果锡禹神龟而负夫九畴乎。仲虺曰。天乃锡王勇智。鲁颂曰。天锡公纯虾。言圣人之▣质。天下之上寿。皆天所赋予。岂必有是物而后。可谓之锡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锡之神禹以为瑞。如箫韶奏而凤仪。春秋作而麟至。则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知。奚必以鲧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畴之纲禹叙之。犹羲文之划卦也。而其目箕子陈之。犹孔子作彖象之辞以明易也。武王访之。犹访太公而受丹书也。天以是理锡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畴。以垂示万世。为不刊之经。岂有诡异神奇之事乎。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龙图发。洛书龟感。又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夫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而已。岂尝言龟龙之事乎。又乌有所
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后。九畴可得而施。此彝伦所为叙也。彝伦之叙。即九畴之叙者也。盖洪范九畴。原出于天。鲧逆水性。汩陈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顺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锡之耳。先言帝不畀鲧。而后言天锡禹。则可见所谓畀所谓锡者。即九畴所陈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验。有迹之可求。岂曰平水之后。天果锡禹神龟而负夫九畴乎。仲虺曰。天乃锡王勇智。鲁颂曰。天锡公纯虾。言圣人之▣质。天下之上寿。皆天所赋予。岂必有是物而后。可谓之锡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锡之神禹以为瑞。如箫韶奏而凤仪。春秋作而麟至。则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知。奚必以鲧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畴之纲禹叙之。犹羲文之划卦也。而其目箕子陈之。犹孔子作彖象之辞以明易也。武王访之。犹访太公而受丹书也。天以是理锡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畴。以垂示万世。为不刊之经。岂有诡异神奇之事乎。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龙图发。洛书龟感。又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夫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而已。岂尝言龟龙之事乎。又乌有所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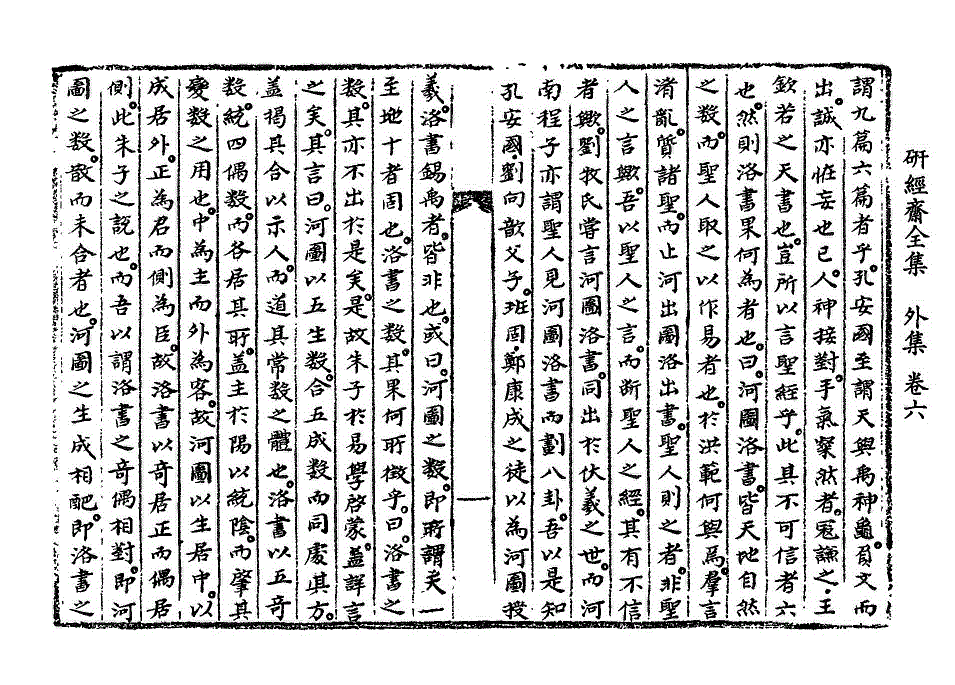 谓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国至谓天与禹神龟。负文而出。诚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对。手气粲然者。寇谦之,王钦若之天书也。岂所以言圣经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则洛书果何为者也。曰。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范何与焉。群言淆乱。质诸圣。而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非圣人之言欤。吾以圣人之言。而断圣人之经。其有不信者欤。刘牧氏尝言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划八卦。吾以是知孔安国,刘向歆父子。班固,郑康成之徒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图之数。即所谓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书之数。其果何所徵乎。曰。洛书之数。其亦不出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学启蒙。盖详言之矣。其言曰。河图以五生数。合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合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中为主而外为客。故河图以生居中。以成居外。正为君而侧为臣。故洛书以奇居正而偶居侧。此朱子之说也。而吾以谓洛书之奇偶相对。即河图之数。散而未合者也。河图之生成相配。即洛书之
谓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国至谓天与禹神龟。负文而出。诚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对。手气粲然者。寇谦之,王钦若之天书也。岂所以言圣经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则洛书果何为者也。曰。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范何与焉。群言淆乱。质诸圣。而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非圣人之言欤。吾以圣人之言。而断圣人之经。其有不信者欤。刘牧氏尝言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划八卦。吾以是知孔安国,刘向歆父子。班固,郑康成之徒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图之数。即所谓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书之数。其果何所徵乎。曰。洛书之数。其亦不出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学启蒙。盖详言之矣。其言曰。河图以五生数。合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合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中为主而外为客。故河图以生居中。以成居外。正为君而侧为臣。故洛书以奇居正而偶居侧。此朱子之说也。而吾以谓洛书之奇偶相对。即河图之数。散而未合者也。河图之生成相配。即洛书之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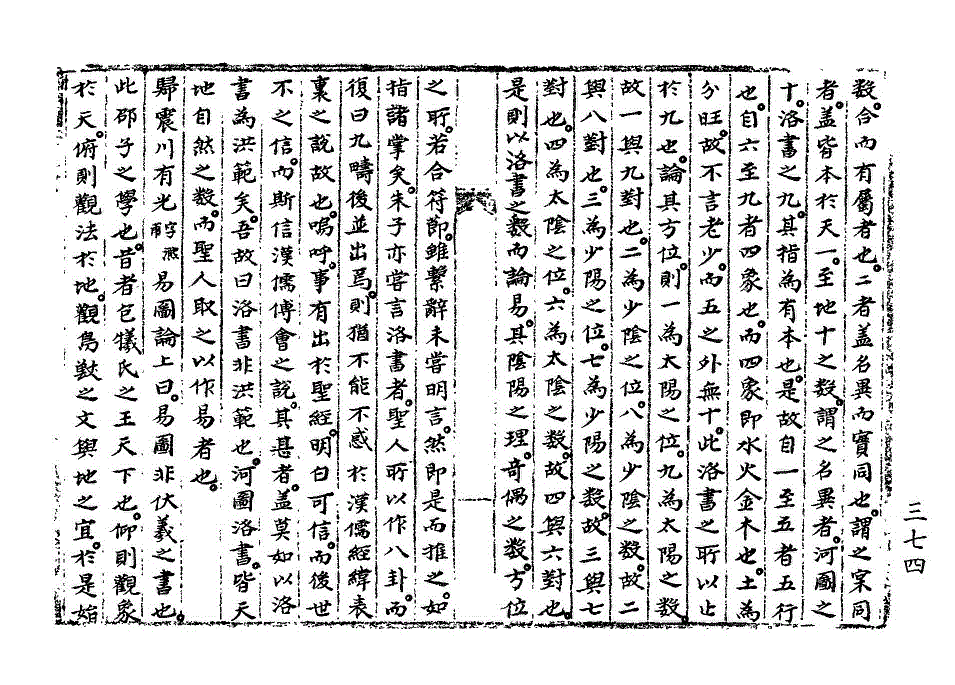 数。合而有属者也。二者盖名异而实同也。谓之宲同者。盖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数。谓之名异者。河图之十。洛书之九。其指为有本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无十。此洛书之所以止于九也。论其方位。则一为太阳之位。九为太阳之数。故一与九对也。二为少阴之位。八为少阴之数。故二与八对也。三为少阳之位。七为少阳之数。故三与七对也。四为太阴之位。六为太阴之数。故四与六对也。是则以洛书之数而论易。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方位之所。若合符节。虽系辞未尝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诸掌矣。朱子亦尝言洛书者。圣人所以作八卦。而复曰九畴后并出焉。则犹不能不惑于汉儒经纬表里之说故也。呜呼。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不之信。而斯信汉儒傅会之说。其甚者。盖莫如以洛书为洪范矣。吾故曰洛书非洪范也。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数。合而有属者也。二者盖名异而实同也。谓之宲同者。盖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数。谓之名异者。河图之十。洛书之九。其指为有本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无十。此洛书之所以止于九也。论其方位。则一为太阳之位。九为太阳之数。故一与九对也。二为少阴之位。八为少阴之数。故二与八对也。三为少阳之位。七为少阳之数。故三与七对也。四为太阴之位。六为太阴之数。故四与六对也。是则以洛书之数而论易。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方位之所。若合符节。虽系辞未尝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诸掌矣。朱子亦尝言洛书者。圣人所以作八卦。而复曰九畴后并出焉。则犹不能不惑于汉儒经纬表里之说故也。呜呼。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不之信。而斯信汉儒傅会之说。其甚者。盖莫如以洛书为洪范矣。吾故曰洛书非洪范也。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归震川有光(字熙甫)易图论上曰。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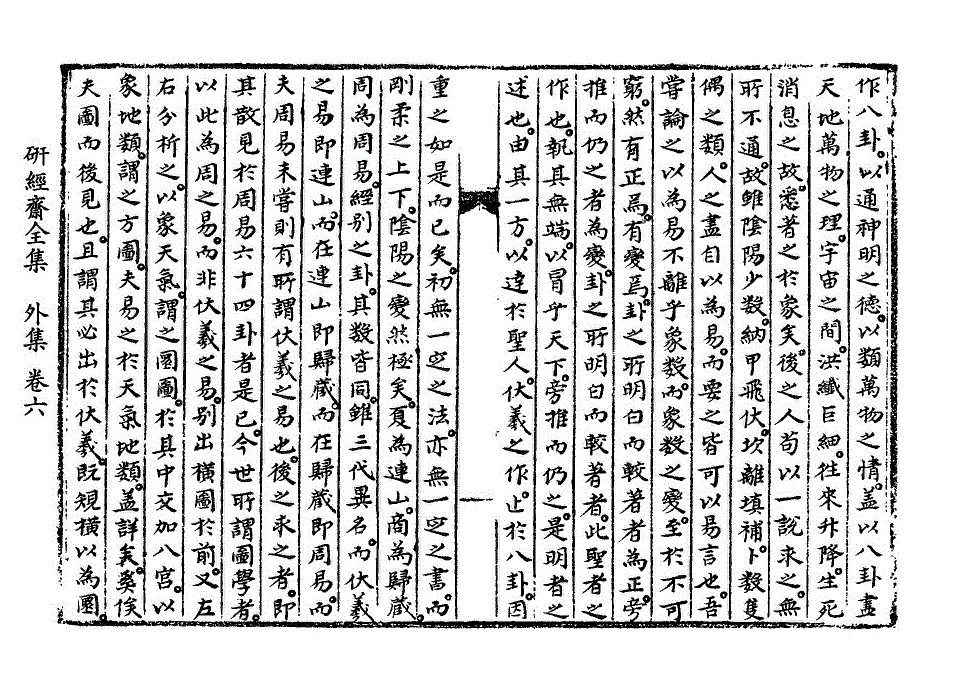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少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之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然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夫周易未尝则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圜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圜。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少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之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然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夫周易未尝则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圜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圜。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5L 页
 文填圜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圜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纷纷耶。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周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于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而皇极经世之书。有分称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
文填圜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圜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纷纷耶。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周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于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而皇极经世之书。有分称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6H 页
 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系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辩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剌。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入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气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不可以不论。又后曰。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那。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剋之序。
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系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辩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剌。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入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气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不可以不论。又后曰。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那。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剋之序。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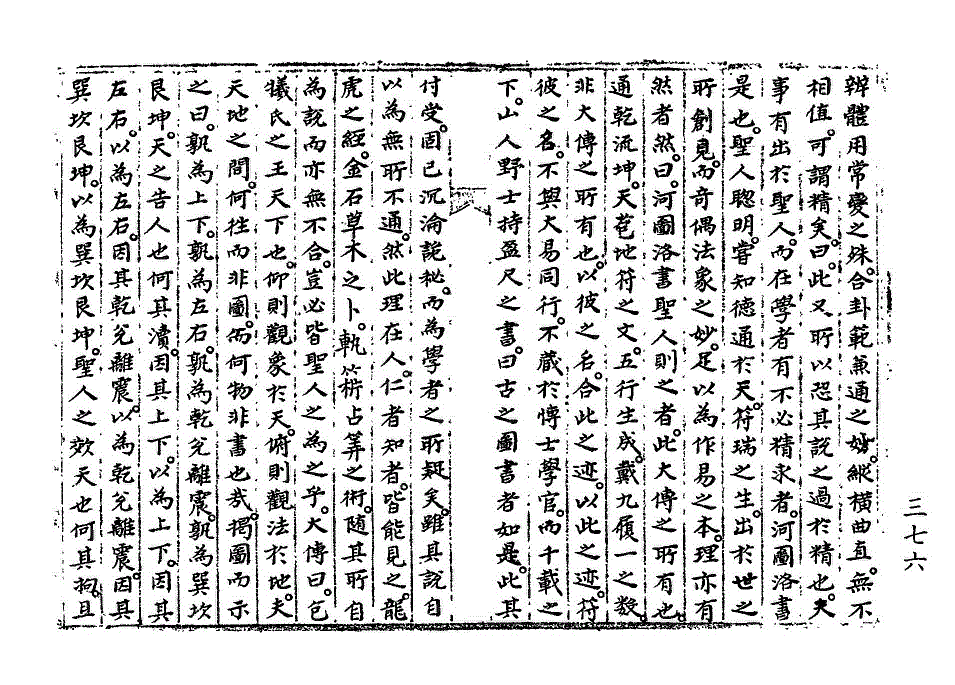 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曰。此又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尝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𥯻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大传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而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乾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乾兑离震。以为乾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
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曰。此又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尝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𥯻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大传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而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乾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乾兑离震。以为乾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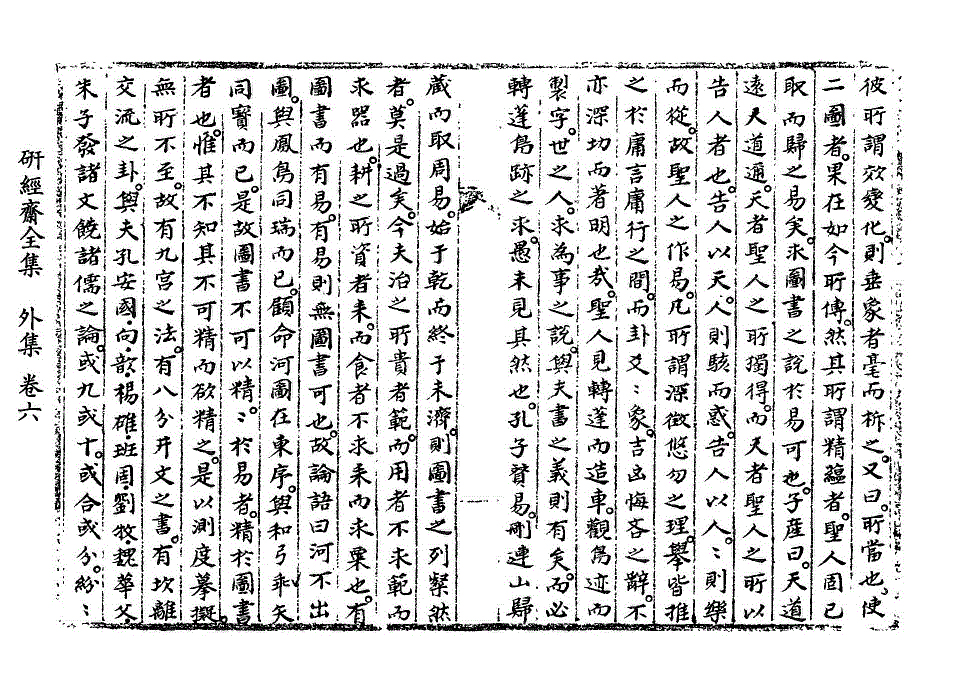 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曰。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徵悠勿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爻象。吉凶悔吝之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事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治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曰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和弓乖(一作垂)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书。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向,歆,杨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诸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
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曰。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徵悠勿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爻象。吉凶悔吝之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事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治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曰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和弓乖(一作垂)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书。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向,歆,杨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诸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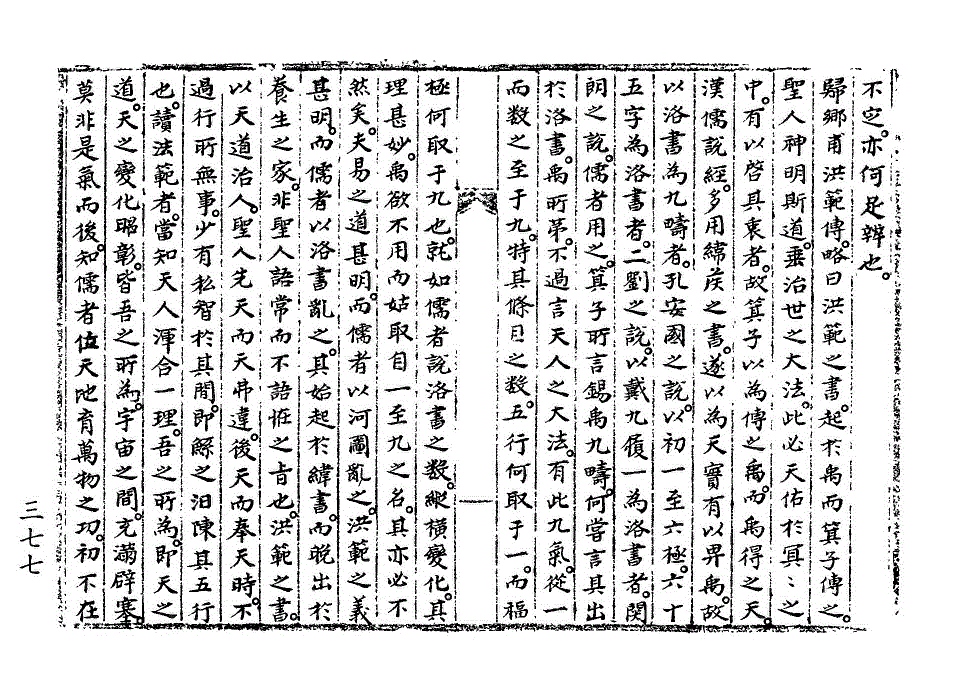 不定。亦何足辨也。
不定。亦何足辨也。归乡甫洪范传。略曰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天。汉儒说经。多用纬侯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气。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欲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汩陈其五行也。读法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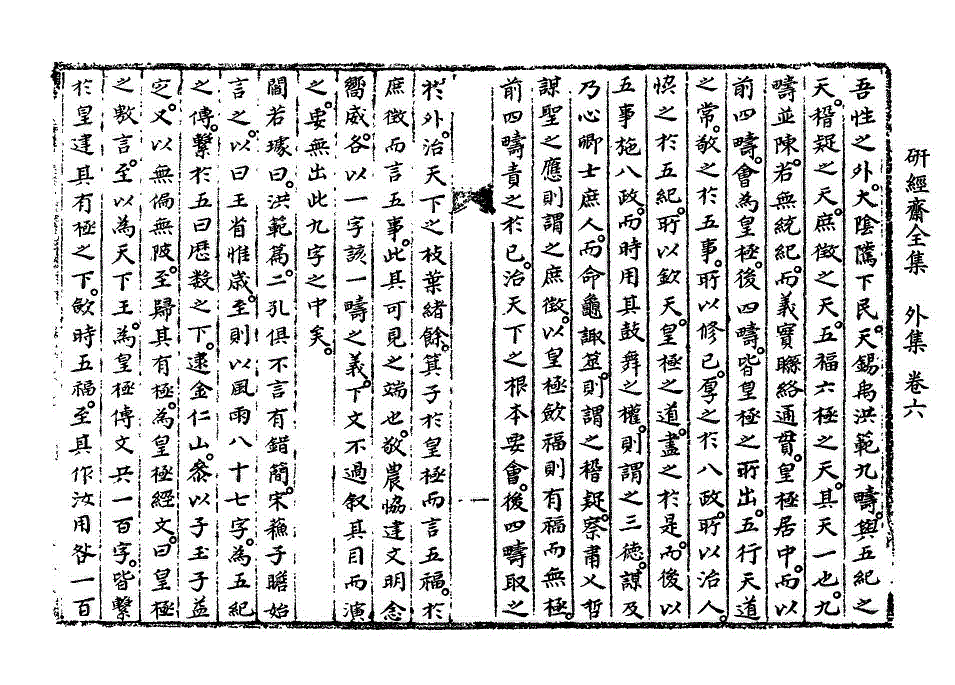 吾性之外。大阴骘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义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协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筮。则谓之稽疑。察肃乂哲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徵。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馀。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文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
吾性之外。大阴骘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义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协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筮。则谓之稽疑。察肃乂哲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徵。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馀。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文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阎若璩曰。洪范篇。二孔俱不言有错简。宋苏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八十七字。为五纪之传。系于五曰历数之下。逮金仁山。参以子玉子益定。又以无偏无陂。至归其有极。为皇极经文。曰皇极之敷言。至以为天下王。为皇极传文共一百字。皆系于皇建其有极之下。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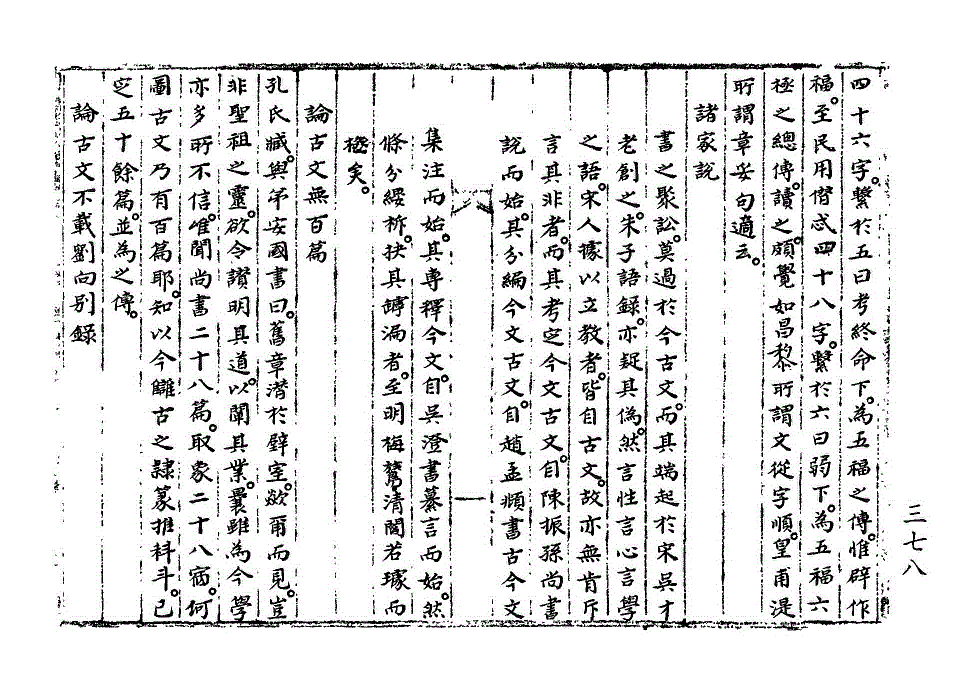 四十六字。系于五曰考终命下。为五福之传。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系于六曰弱下。为五福六极之总传。读之。颇觉如昌黎所谓文从字顺。皇甫湜所谓章妥句适云。
四十六字。系于五曰考终命下。为五福之传。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系于六曰弱下。为五福六极之总传。读之。颇觉如昌黎所谓文从字顺。皇甫湜所谓章妥句适云。诸家说
书之聚讼。莫过于今古文。而其端起于宋吴才老创之。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皆自古文。故亦无肯斥言其非者。而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而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而始。其专释今文。自吴澄书纂言而始。然条分缕析。抉其罅遍(一作漏)者。至明梅鷟,清阎若璩而极矣。
论古文无百篇
孔氏臧。与弟安国书曰。旧章潜于壁室。歘尔而见。岂非圣祖之灵。欲令赞明其道。以阐其业。曩虽为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古文乃有百篇耶。知以今雠古之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馀篇。并为之传。
论古文不载刘向别录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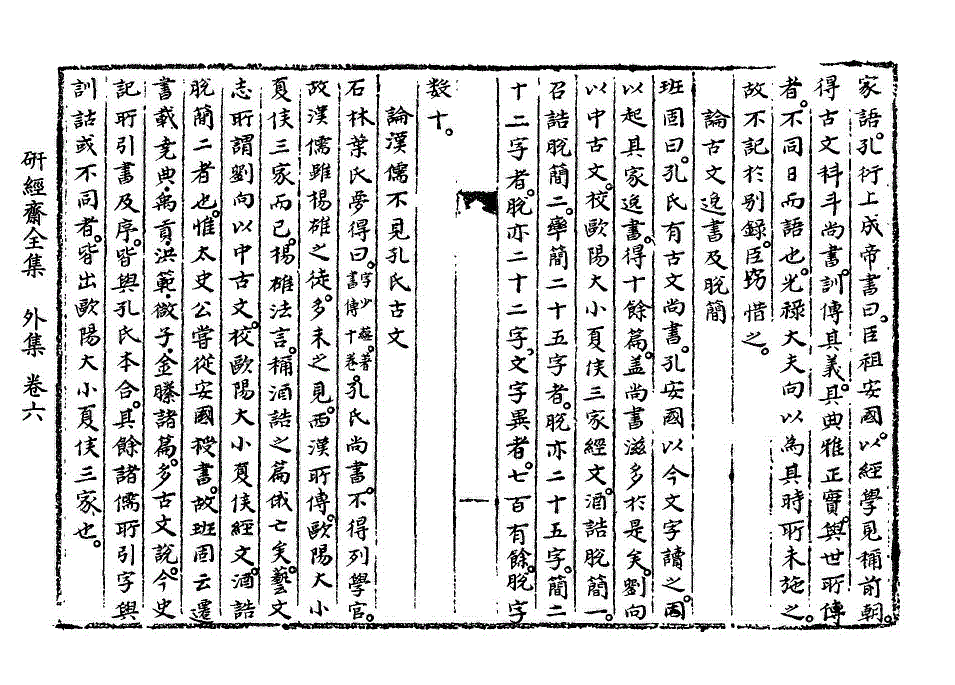 家语。孔衍上成帝书曰。臣祖安国。以经学见称前朝。得古文科斗尚书。训传其义。其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语也。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故不记于别录。臣窃惜之。
家语。孔衍上成帝书曰。臣祖安国。以经学见称前朝。得古文科斗尚书。训传其义。其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语也。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故不记于别录。臣窃惜之。论古文逸书及脱简
班固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
论汉儒不见孔氏古文
石林叶氏梦得曰。(字少蕴。著书传十卷。)孔氏尚书。不得列学官。故汉儒虽杨雄之徒。多未之见。西汉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杨雄法言。称酒诰之篇俄亡矣。艺文志所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二者也。惟太史公尝从安国授书。故班固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今史记所引书及序。皆与孔氏本合。其馀诸儒所引字与训诂或不同者。皆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也。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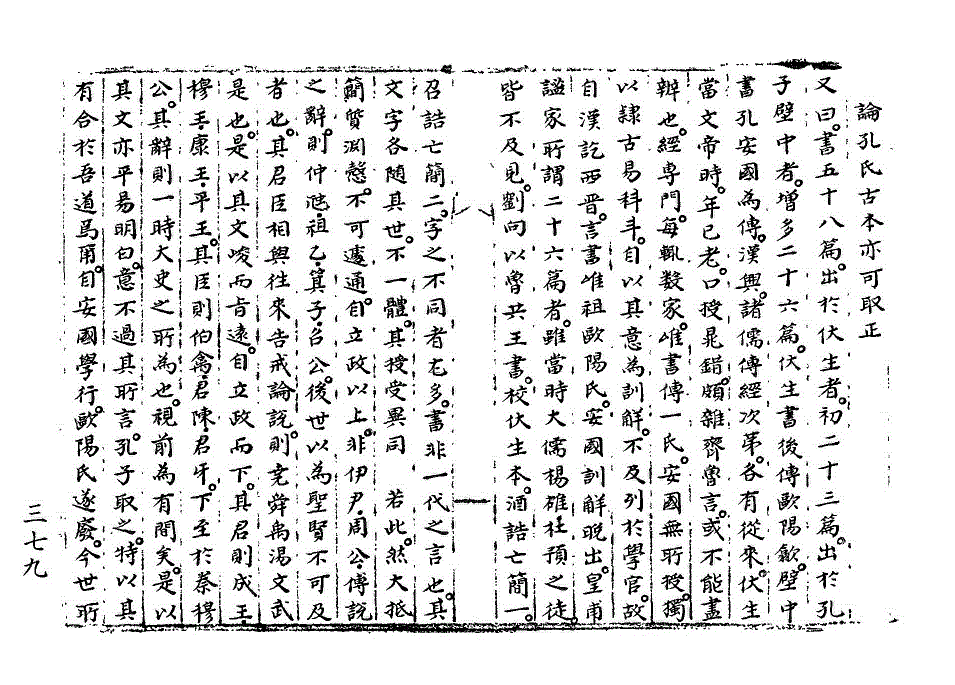 论孔氏古本亦可取正
论孔氏古本亦可取正又曰。书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孔子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后传欧阳歙。壁中书孔安国为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辨也。经专门。每辄数家。唯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于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唯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杨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共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 若此。然大抵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以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后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大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间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0H 页
 见。唯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作于周公殁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予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 劝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误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见。唯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作于周公殁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予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 劝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误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论古文在中秘书
碧梧马氏曰。按孔传所言。则古文书。其经已送之王宫。藏之中秘。其传则遭巫蛊而不复上闻。藏之私家者也。以其未立于学官。是以经伏而传不行于世耳。是则所谓古文书。岂惟未尝逸。盖亦未尝不在王宫也。刘歆移太常书所谓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者是也。中秘书。非世儒所得见。宜乎后之引古文书者。皆不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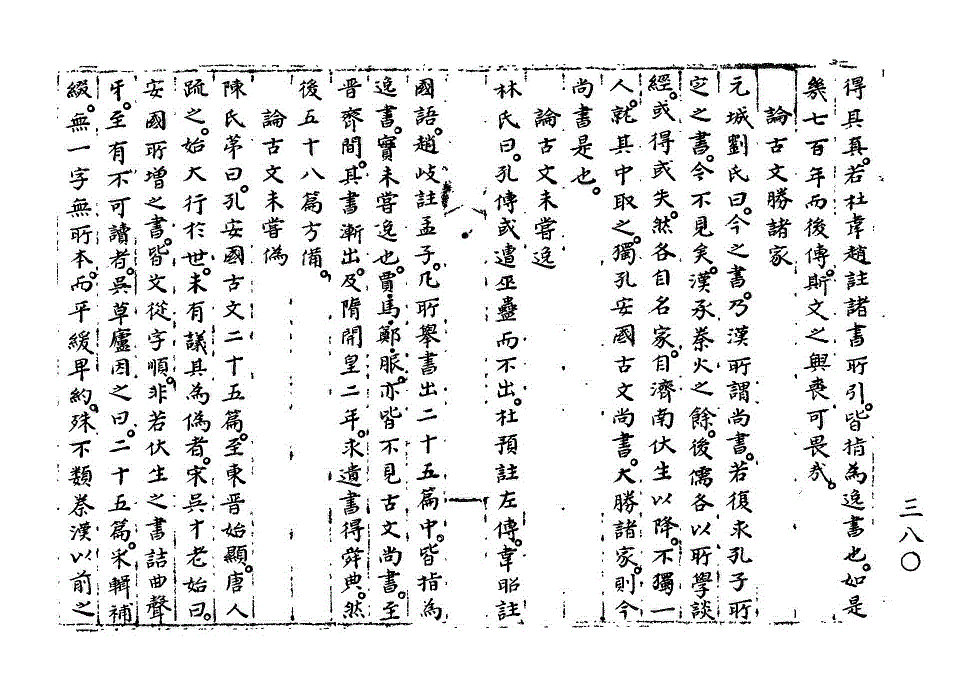 得其真。若杜韦赵注诸书所引。皆指为逸书也。如是几七百年而后传。斯文之兴丧可畏哉。
得其真。若杜韦赵注诸书所引。皆指为逸书也。如是几七百年而后传。斯文之兴丧可畏哉。论古文胜诸家
元城刘氏曰。今之书。乃汉所谓尚书。若复求孔子所定之书。今不见矣。汉承秦火之馀。后儒各以所学谈经。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济南伏生以降。不独一人。就其中取之。独孔安国古文尚书。大胜诸家。则今尚书是也。
论古文未尝逸
林氏曰。孔传或遭巫蛊而不出。杜预注左传。韦昭注国语。赵岐注孟子。凡所举书出二十五篇中。皆指为逸书。实未尝逸也。贾,马,郑,服。亦皆不见古文尚书。至晋齐间。其书渐出。及隋开皇二年。求遗书得舜典。然后五十八篇方备。
论古文未尝伪
陈氏第曰。孔安国古文二十五篇。至东晋始显。唐人疏之。始大行于世。未有议其为伪者。宋吴才老始曰。安国所增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声牙。至有不可读者。吴草庐因之曰。二十五篇。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约。殊不类秦汉以前之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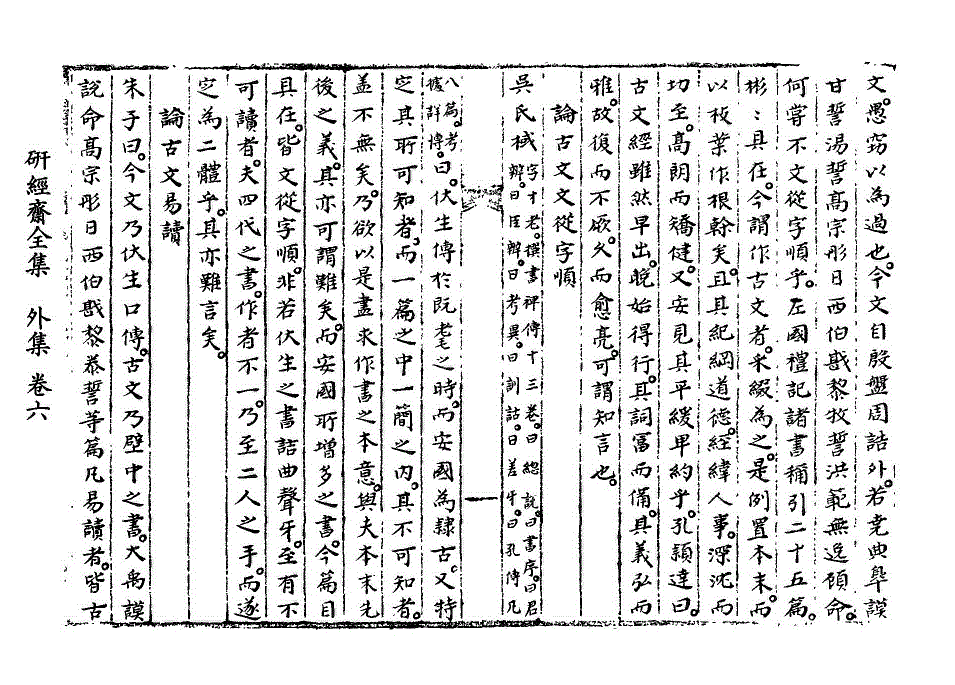 文。愚窃以为过也。今文自殷盘周诰外。若尧典皋谟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何尝不文从字顺乎。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例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干矣。且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矫健。又安见其平缓卑约乎。孔颖达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词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厥。久而愈亮。可谓知言也。
文。愚窃以为过也。今文自殷盘周诰外。若尧典皋谟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何尝不文从字顺乎。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例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干矣。且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矫健。又安见其平缓卑约乎。孔颖达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词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厥。久而愈亮。可谓知言也。论古文文从字顺
吴氏棫(字才老。撰书裨传十三卷。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训诂。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
论古文易读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大禹谟说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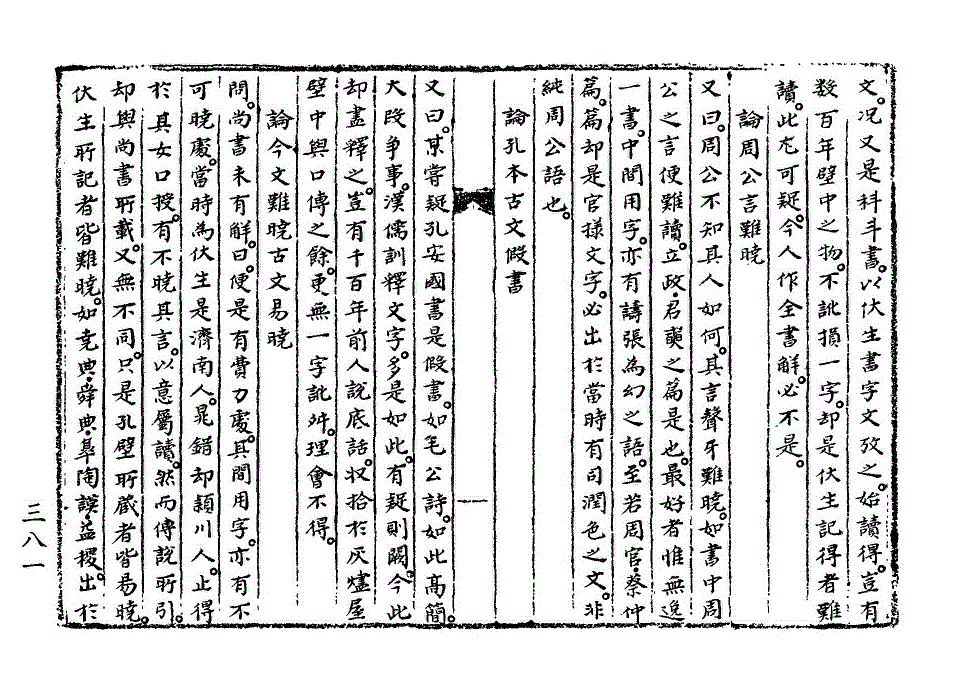 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始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
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始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论周公言难晓
又曰。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难晓。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篇。篇却是官㨾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
论孔本古文假书
又曰。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如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
论今文难晓古文易晓
问。尚书未有解。曰。便是有费力处。其间用字。亦有不可晓处。当时为伏生是济南人。晁错却颖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然而传说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晓。伏生所记者皆难晓。如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出于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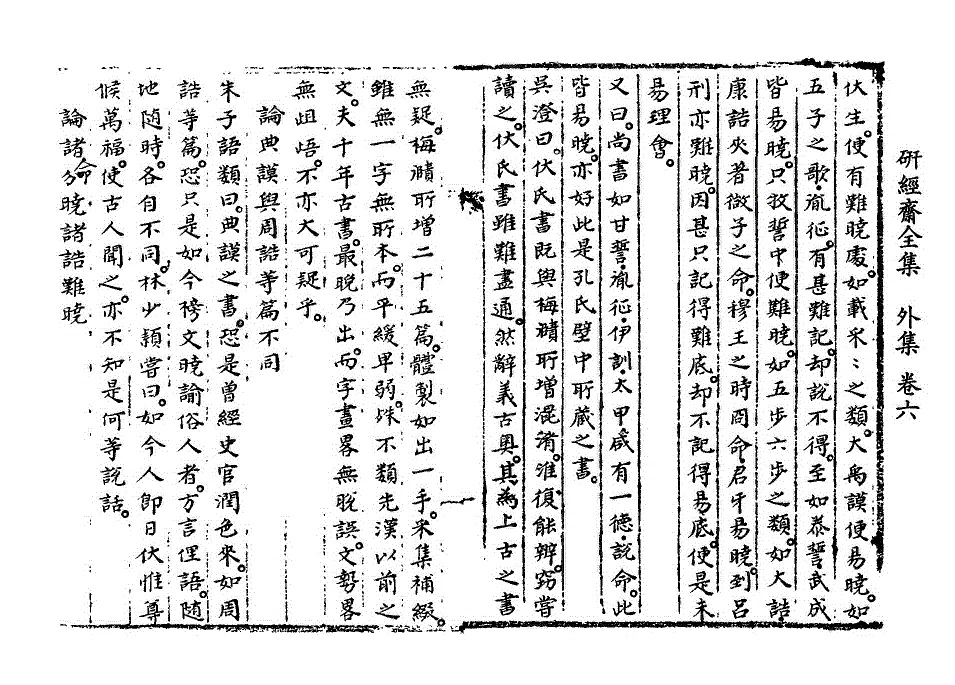 伏生。便有难晓处。如载采采之类。大禹谟便易晓。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难记。却说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晓。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时囧命,君牙易晓。到吕刑亦难晓。因甚只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便是未易理会。
伏生。便有难晓处。如载采采之类。大禹谟便易晓。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难记。却说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晓。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时囧命,君牙易晓。到吕刑亦难晓。因甚只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便是未易理会。又曰。尚书如甘誓,胤征,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此皆易晓。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书。
吴澄曰。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混淆。淮复能辨。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
论典谟与周诰等篇不同
朱子语类曰。典谟之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如周诰等篇。恐只是如今榜文晓谕俗人者。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林少颖尝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万福。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
论诸命分晓诸诰难晓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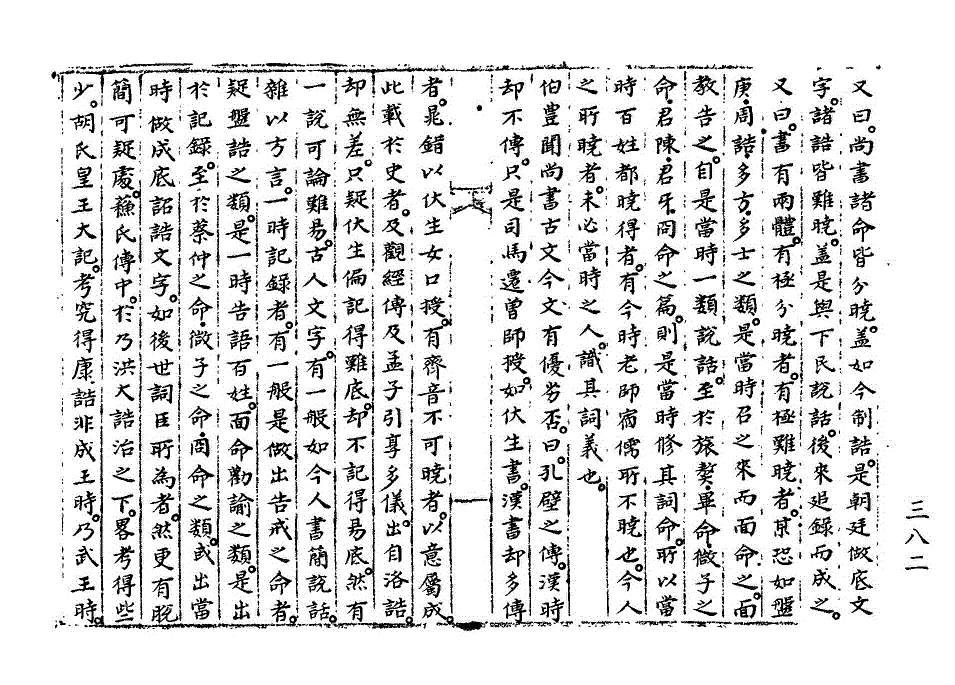 又曰。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与下民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
又曰。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与下民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某恐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囧命之篇。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所不晓也。今人之所晓者。未必当时之人。识其词义也。
伯礼闻尚书古文今文有优劣否。曰。孔壁之传。汉时却不传。只是司马迁曾师授。如伏生书。汉书却多传者。晁错以伏生女口授。有齐音不可晓者。以意属成。此载于史者。及观经传及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只疑伏生偏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然有一说可论难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书简说话。杂以方言。一时记录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盘诰之类。是一时告语百姓。面命劝谕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囧命之类。或出当时做成底诏诰文字。如后世词臣所为者。然更有脱简可疑处。苏氏传中。于乃洪大诰治之下。略考得些少。胡氏皇王大记。考究得康诰非成王时。乃武王时。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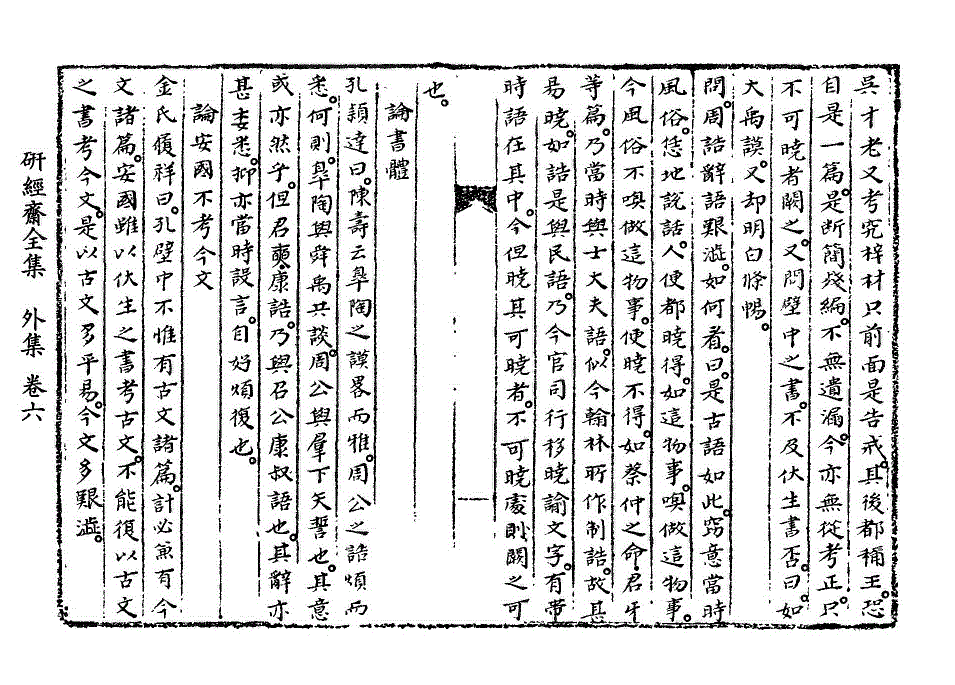 吴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后都称王。恐自是一篇。是断简残编。不无遗漏。今亦无从考正。只不可晓者阙之。又问壁中之书。不及伏生书否。曰。如大禹谟。又却明白条畅。
吴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后都称王。恐自是一篇。是断简残编。不无遗漏。今亦无从考正。只不可晓者阙之。又问壁中之书。不及伏生书否。曰。如大禹谟。又却明白条畅。问。周诰辞语艰涩。如何看。曰。是古语如此。窃意当时风俗。恁地说话。人便都晓得。如这物事。唤做这物事。今风俗不唤做这物事。便晓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当时与士大夫语。似今翰林所作制诰。故甚易晓。如诰是与民语。乃今官司行移晓谕文字。有带时语在其中。今但晓其可晓者。不可晓处则阙之可也。
论书体
孔颖达曰。陈寿云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诰。乃与召公康叔语也。其辞亦甚委悉。抑亦当时设言。自好烦复也。
论安国不考今文
金氏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诸篇。计必兼有今文诸篇。安国虽以伏生之书考古文。不能复以古文之书考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涩。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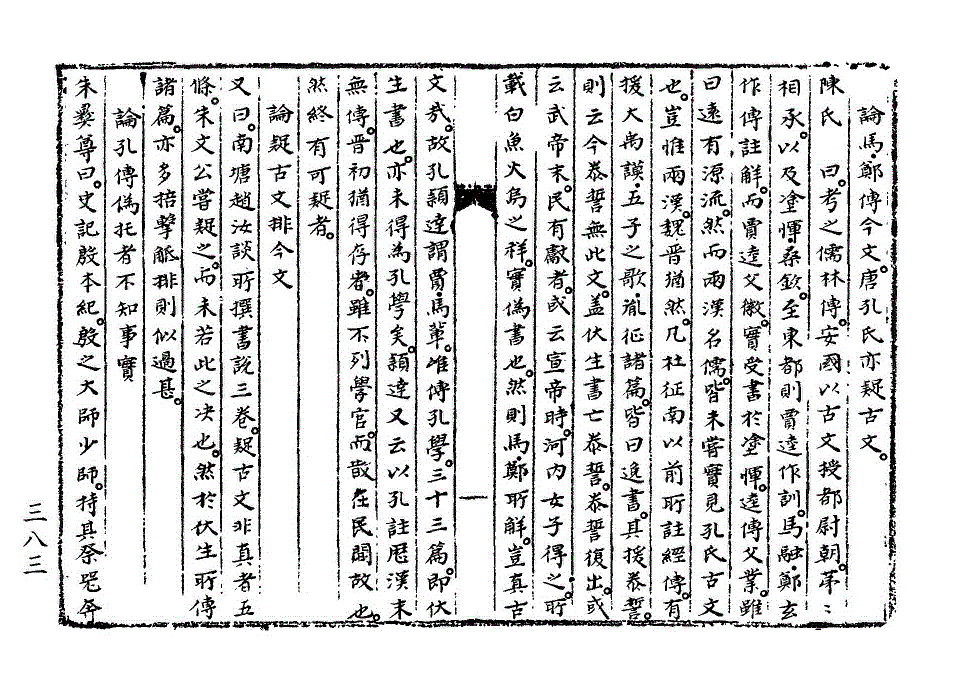 论马,郑传今文。唐孔氏亦疑古文。
论马,郑传今文。唐孔氏亦疑古文。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玄作传注解。而贾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复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唯传孔学。三十三篇。即伏生书也。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也。然终有可疑者。
论疑古文排今文
又曰。南塘赵汝谈所撰书说三卷。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掊击抵排则似过甚。
论孔传伪托者不知事实
朱彝尊曰。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持其祭器奔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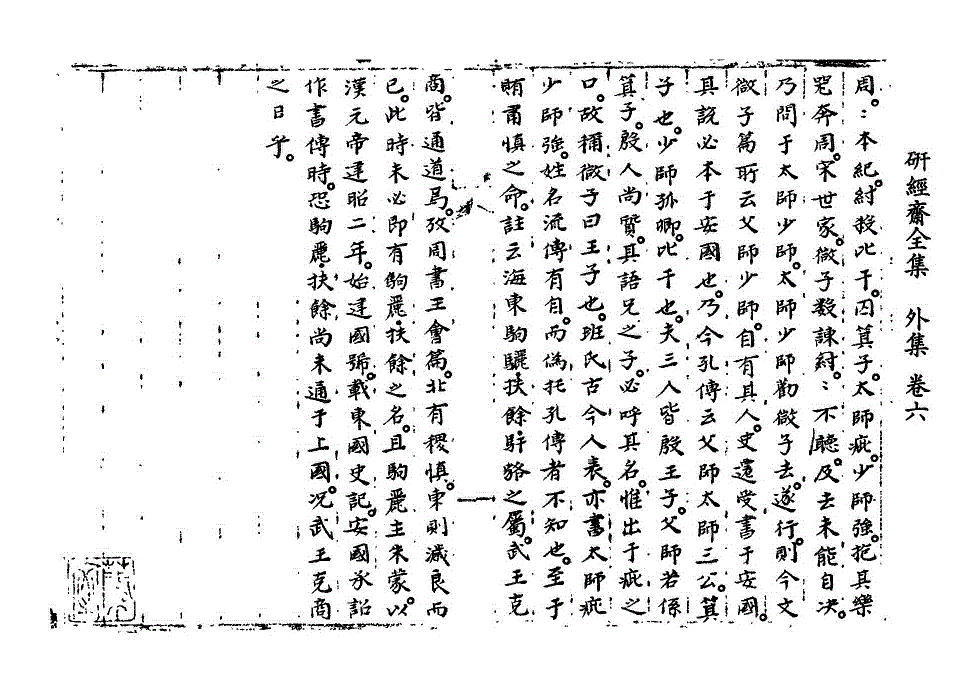 周。周本纪。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数谏纣。纣不听。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去。遂行。则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史迁受书于安国。其说必本于安国也。乃今孔传云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夫三人皆殷王子。父师若系箕子。殷人尚质。其语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称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书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自。而伪托孔传者不知也。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云海东驹骊,扶馀,馯貉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丽,扶馀之名。且驹丽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记。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丽,扶馀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周。周本纪。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数谏纣。纣不听。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去。遂行。则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史迁受书于安国。其说必本于安国也。乃今孔传云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夫三人皆殷王子。父师若系箕子。殷人尚质。其语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称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书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自。而伪托孔传者不知也。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云海东驹骊,扶馀,馯貉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丽,扶馀之名。且驹丽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记。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丽,扶馀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