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经解三
经解三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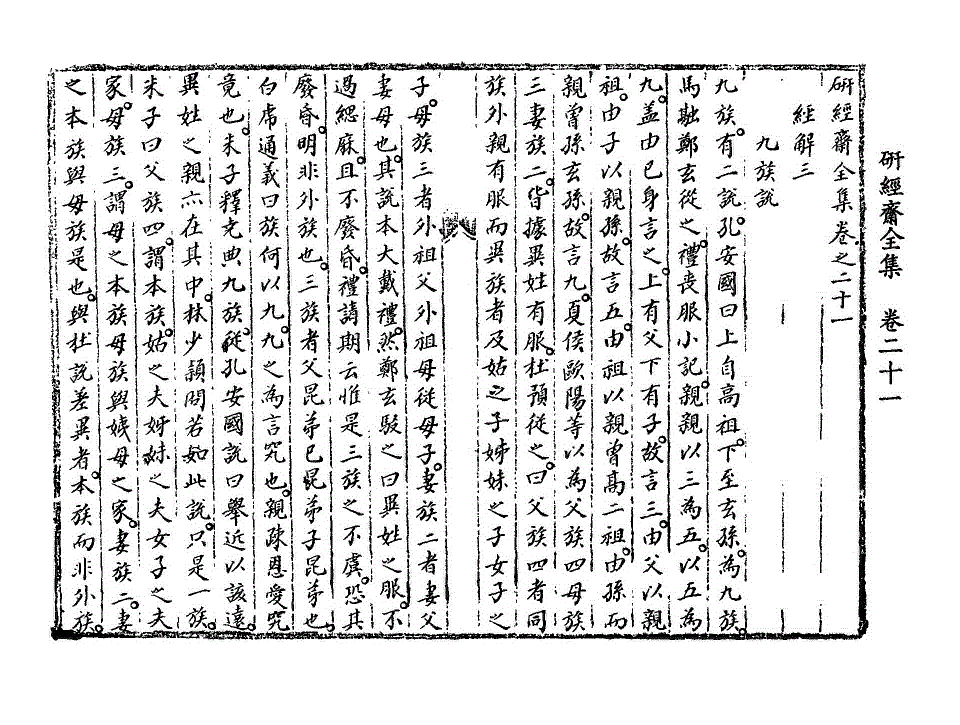 九族说
九族说九族。有二说。孔安国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马融郑玄从之。礼丧服小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盖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故言三。由父以亲祖。由子以亲孙。故言五。由祖以亲曾高二祖。由孙而亲曾孙玄孙。故言九。夏侯欧阳等以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据异姓有服。杜预从之。曰父族四者同族外亲有服而异族者及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母族三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族二者妻父妻母也。其说本大戴礼。然郑玄驳之曰异姓之服。不过缌麻。且不废昏。礼请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废昏。明非外族也。三族者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白虎通义曰族何以九。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也。朱子释尧典九族。从孔安国说曰举近以该远。异姓之亲亦在其中。林少颖问若如此说。只是一族。朱子曰父族四。谓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三。谓母之本族母族与姨母之家。妻族二。妻之本族与母族是也。与杜说差异者。本族而非外族。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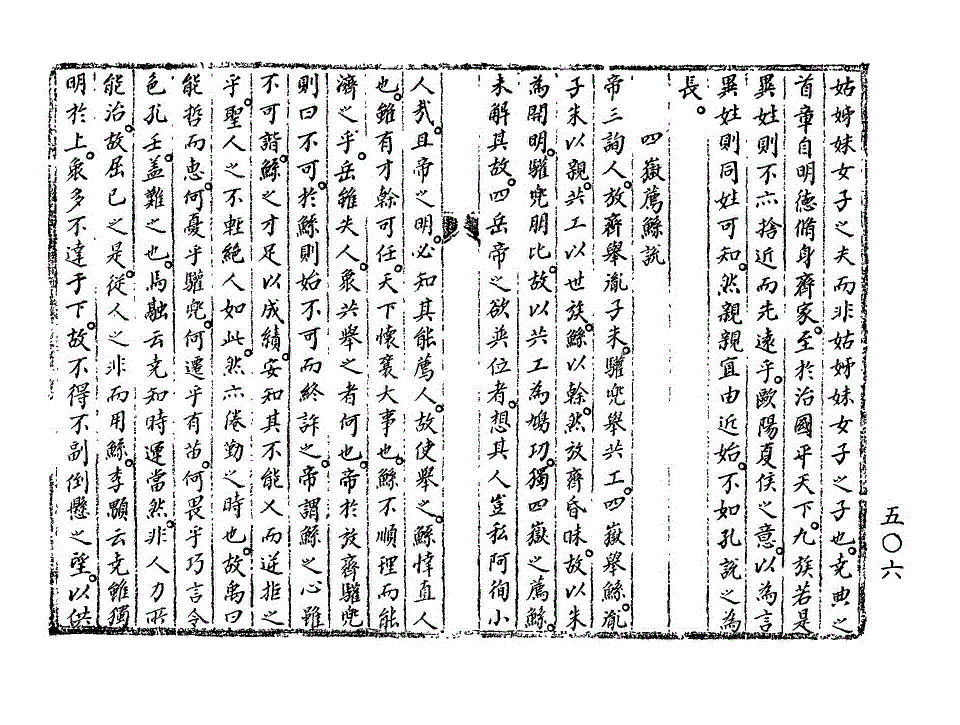 姑姊妹女子之夫而非姑姊妹女子之子也。尧典之首章自明德脩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九族若是异姓则不亦舍近而先远乎。欧阳夏侯之意。以为言异姓则同姓可知。然亲亲宜由近始。不如孔说之为长。
姑姊妹女子之夫而非姑姊妹女子之子也。尧典之首章自明德脩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九族若是异姓则不亦舍近而先远乎。欧阳夏侯之意。以为言异姓则同姓可知。然亲亲宜由近始。不如孔说之为长。四岳荐鲧说
帝三询人。放齐举胤子朱。驩兜举共工。四岳举鲧。胤子朱以亲。共工以世族。鲧以干。然放齐昏昧。故以朱为开明。驩兜朋比。故以共工为鸠功。独四岳之荐鲧。未解其故。四岳帝之欲巽位者。想其人岂私阿徇小人哉。且帝之明。必知其能荐人。故使举之。鲧悻直人也。虽有才干可任。天下怀襄大事也。鲧不顺理而能济之乎。岳虽失人。众共举之者何也。帝于放齐驩兜则曰不可。于鲧则始不可而终许之。帝谓鲧之心虽不可谐。鲧之才足以成绩。安知其不能乂而逆拒之乎。圣人之不轻绝人如此。然亦倦勤之时也。故禹曰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盖难之也。马融云尧知时运当然。非人力所能治。故屈己之是。从人之非而用鲧。李颙云尧虽独明于上。众多不达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悬之望。以供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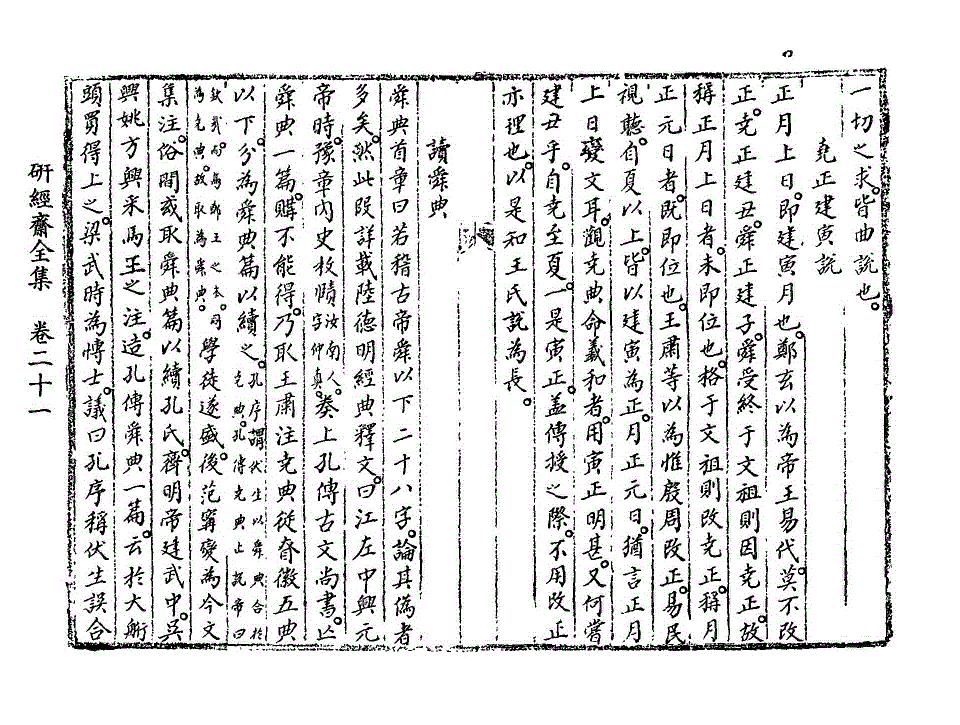 一切之求。皆曲说也。
一切之求。皆曲说也。尧正建寅说
正月上日。即建寅月也。郑玄以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舜受终于文祖则因尧正。故称正月上日者。未即位也。格于文祖则改尧正。称月正元日者。既即位也。王肃等以为惟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月正元日。犹言正月上日变文耳。观尧典命羲和者。用寅正明甚。又何尝建丑乎。自尧至夏。一是寅正。盖传授之际。不用改正亦理也。以是知王氏说为长。
读舜典
舜典首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论其伪者多矣。然此段详载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汝南人。字仲真。)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孔序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止说帝曰钦哉。而马郑王之本。同为尧典。故取为舜典。)学徒遂盛。后范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𦨵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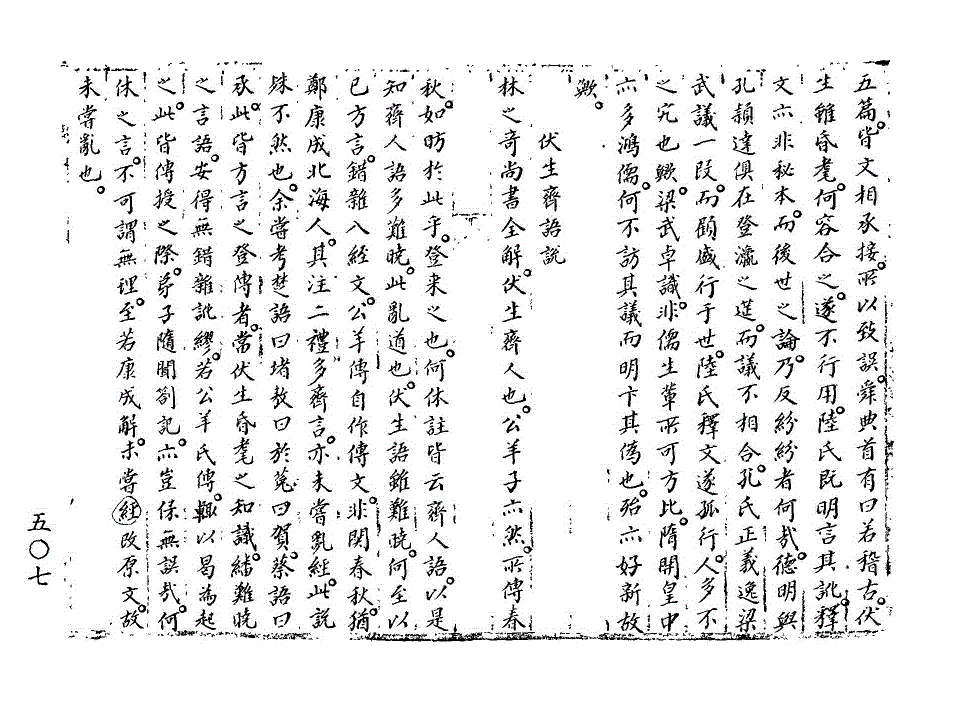 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陆氏既明言其讹。释文亦非秘本。而后世之论。乃反纷纷者何哉。德明与孔颖达俱在登瀛之筵。而议不相合。孔氏正义逸梁武议一段。而顾盛行于世。陆氏释文遂孤行。人多不之宄也欤。梁武卓识。非儒生辈所可方比。隋开皇中亦多鸿儒。何不访其议而明卞其伪也。殆亦好新故欤。
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陆氏既明言其讹。释文亦非秘本。而后世之论。乃反纷纷者何哉。德明与孔颖达俱在登瀛之筵。而议不相合。孔氏正义逸梁武议一段。而顾盛行于世。陆氏释文遂孤行。人多不之宄也欤。梁武卓识。非儒生辈所可方比。隋开皇中亦多鸿儒。何不访其议而明卞其伪也。殆亦好新故欤。伏生齐语说
林之奇尚书全解。伏生齐人也。公羊子亦然。所传春秋。如昉于此乎。登来之也。何休注皆云齐人语。以是知齐人语多难晓。此乱道也。伏生语虽难晓。何至以己方言。错杂入经文。公羊传自作传文。非关春秋。犹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二礼多齐言。亦未尝乱经。此说殊不然也。余尝考楚语曰堵敖曰于菟曰贺。蔡语曰承。此皆方言之登传者。当伏生昏耄之知识。翻难晓之言语。安得无错杂讹缪。若公羊氏传。辄以曷为起之。此皆传授之际。弟子随闻劄记。亦岂保无误哉。何休之言。不可谓无理。至若康成解。未尝经改原文。故未尝乱也。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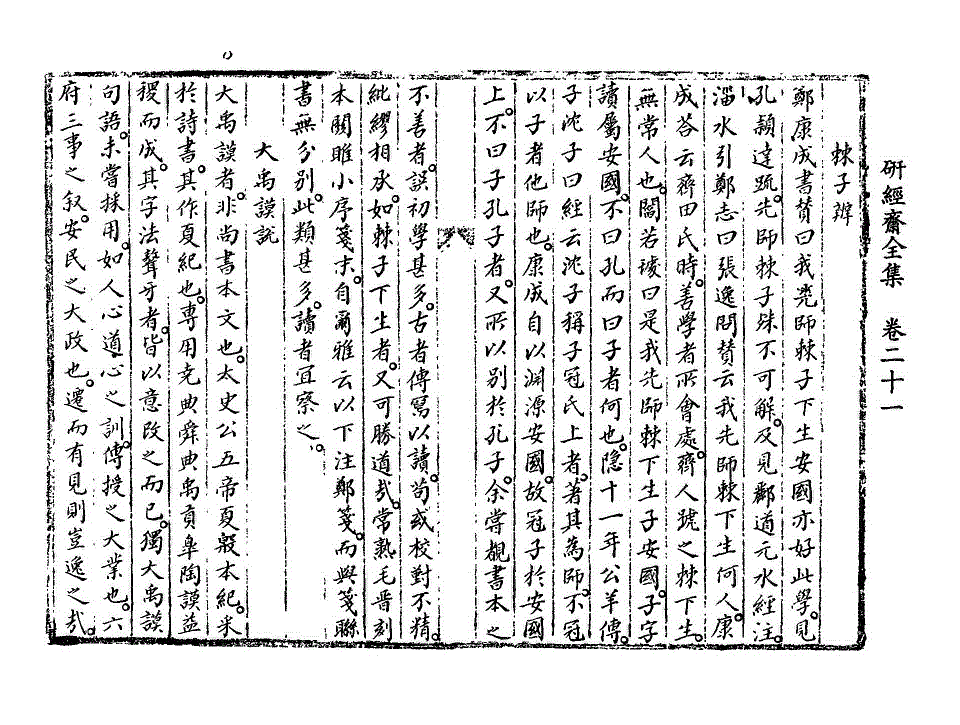 棘子辨
棘子辨郑康成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见孔颖达疏。先师棘子殊不可解。及见郦道元水经注。淄水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人。康成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阎若璩曰是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子字读属安国。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隐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经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不冠以子者他师也。康成自以渊源安国。故冠子于安国上。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别于孔子。余尝睹书本之不善者。误初学甚多。古者传写以读。苟或校对不精。纰缪相承。如棘子下生者。又可胜道哉。常熟毛晋刻本关雎小序笺末。自尔雅云以下注郑笺。而与笺联书无分别。此类甚多。读者宜察之。
大禹谟说
大禹谟者。非尚书本文也。太史公五帝夏殷本纪。采于诗书。其作夏纪也。专用尧典舜典禹贡皋陶谟益稷而成。其字法声牙者。皆以意改之而已。独大禹谟句语。未尝采用。如人心道心之训。传授之大业也。六府三事之叙。安民之大政也。迁而有见则岂逸之哉。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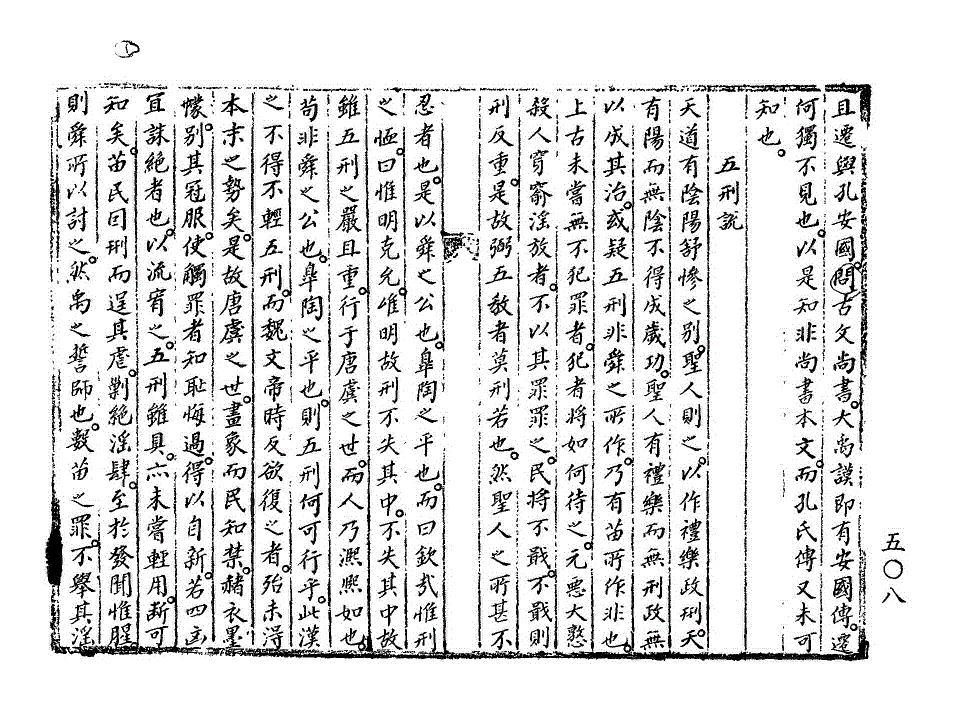 且迁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大禹谟即有安国传。迁何独不见也。以是知非尚书本文。而孔氏传又未可知也。
且迁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大禹谟即有安国传。迁何独不见也。以是知非尚书本文。而孔氏传又未可知也。五刑说
天道有阴阳舒惨之别。圣人则之。以作礼乐政刑。天有阳而无阴不得成岁功。圣人有礼乐而无刑政无以成其治。或疑五刑非舜之所作。乃有苗所作非也。上古未尝无不犯罪者。犯者将如何待之。元恶大憝杀人穿窬淫放者。不以其罪罪之。民将不戢。不戢则刑反重。是故弼五教者莫刑若也。然圣人之所甚不忍者也。是以舜之公也。皋陶之平也。而曰钦哉惟刑之恤。曰惟明克允。唯明故刑不失其中。不失其中故虽五刑之严且重。行于唐虞之世。而人乃熙熙如也。苟非舜之公也。皋陶之平也。则五刑何可行乎。此汉之不得不轻五刑。而魏文帝时反欲复之者。殆未得本末之势矣。是故唐虞之世。画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别其冠服。使触罪者知耻悔过。得以自新。若四凶宜诛绝者也。以流宥之。五刑虽具。亦未尝轻用。断可知矣。苗民因刑而逞其虐。剿绝淫肆。至于发闻惟腥。则舜所以讨之。然禹之誓师也。数苗之罪。不举其淫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9H 页
 刑。是又可疑也。
刑。是又可疑也。读汉石经
汉熹平中石经。即蔡邕所书。称一字石经。魏正始中石经。邯郸淳所书。即三字石经。二石经屡经兵乱。皆不全。独唐开成中石经。在今西安府。金仁山云汉石经洪范文。只曰五行。而不曰一五行。馀传首句。并不言畴数。汉石经即欧阳夏侯所传授。而号称今文者也。今考汉石经残字。有三德一曰之文。据此可见金氏之言确矣。且湮洪水作伊鸿水。汩陈作曰陈。乂用作艾用。而家凶于作而家而凶于。即其残字而不同如此。全文之大有参差可知。且太史公史记引洪范。虽有改字。全篇尽载。而亦不及畴数。且言九畴之纲。亦无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等字。独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迁史亦有所本。且汉石经从鲁诗。故魏风之三岁贯女作宦女。唐风之山有枢作山有蓲。自孔氏正义以后。书从古文。诗从毛诗。然诗则固有所本。书则全无所据。自汉魏至唐。其间三百馀年。而经文之窜乱如此。未知增删者谁欤。极可叹也。
诗周召分圣贤说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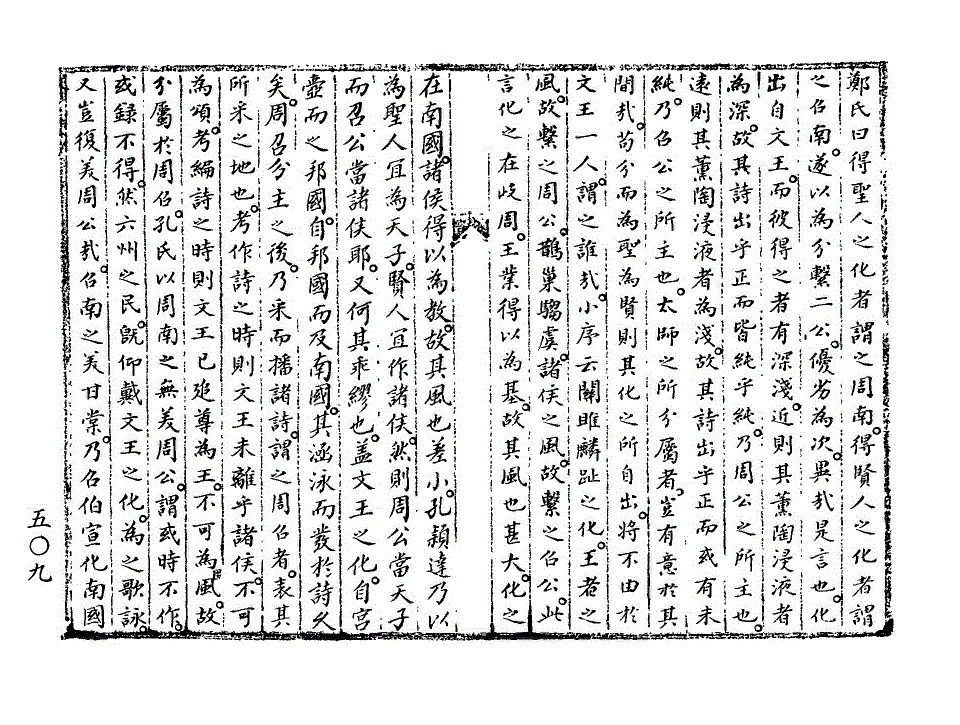 郑氏曰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遂以为分系二公。优劣为次。异哉是言也。化出自文王。而彼得之者有深浅。近则其薰陶浸液者为深。故其诗出乎正而皆纯乎纯。乃周公之所主也。远则其薰陶浸液者为浅。故其诗出乎正而或有未纯。乃召公之所主也。太师之所分属者。岂有意于其间哉。苟分而为圣为贤则其化之所自出。将不由于文王一人。谓之谁哉。小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此言化之在岐周。王业得以为基。故其风也甚大。化之在南国。诸侯得以为教。故其风也差小。孔颖达乃以为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然则周公当天子而召公当诸侯耶。又何其乖缪也。盖文王之化。自宫壸而之邦国。自邦国而及南国。其涵泳而发于诗久矣。周召分主之后。乃采而播诸诗。谓之周召者。表其所采之地也。考作诗之时则文王未离乎诸侯。不可为颂。考编诗之时则文王已追尊为王。不可为周风。故分属于周召。孔氏以周南之无美周公。谓或时不作。或录不得。然六州之民。既仰戴文王之化。为之歌咏。又岂复美周公哉。召南之美甘棠。乃召伯宣化南国
郑氏曰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遂以为分系二公。优劣为次。异哉是言也。化出自文王。而彼得之者有深浅。近则其薰陶浸液者为深。故其诗出乎正而皆纯乎纯。乃周公之所主也。远则其薰陶浸液者为浅。故其诗出乎正而或有未纯。乃召公之所主也。太师之所分属者。岂有意于其间哉。苟分而为圣为贤则其化之所自出。将不由于文王一人。谓之谁哉。小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此言化之在岐周。王业得以为基。故其风也甚大。化之在南国。诸侯得以为教。故其风也差小。孔颖达乃以为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然则周公当天子而召公当诸侯耶。又何其乖缪也。盖文王之化。自宫壸而之邦国。自邦国而及南国。其涵泳而发于诗久矣。周召分主之后。乃采而播诸诗。谓之周召者。表其所采之地也。考作诗之时则文王未离乎诸侯。不可为颂。考编诗之时则文王已追尊为王。不可为周风。故分属于周召。孔氏以周南之无美周公。谓或时不作。或录不得。然六州之民。既仰戴文王之化。为之歌咏。又岂复美周公哉。召南之美甘棠。乃召伯宣化南国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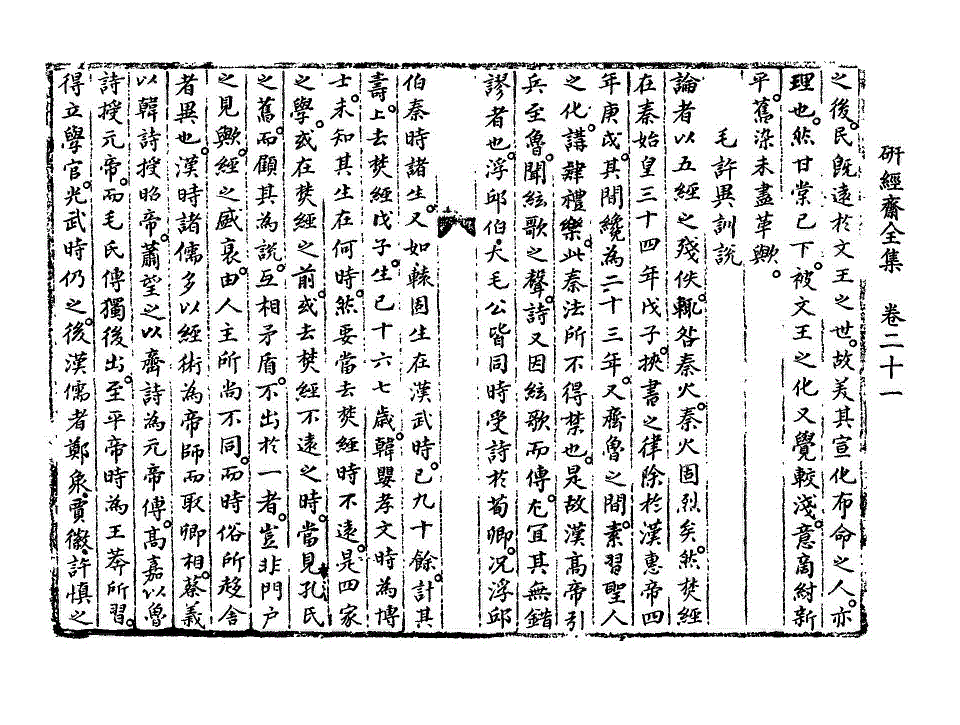 之后。民既远于文王之世。故美其宣化布命之人。亦理也。然甘棠已下。被文王之化又觉较浅。意商纣新平。旧染未尽革欤。
之后。民既远于文王之世。故美其宣化布命之人。亦理也。然甘棠已下。被文王之化又觉较浅。意商纣新平。旧染未尽革欤。毛许异训说
论者以五经之残佚。辄咎秦火。秦火固烈矣。然焚经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戊子。挟书之律除于汉惠帝四年庚戌。其间才为二十三年。又齐鲁之间。素习圣人之化。讲肄礼乐。此秦法所不得禁也。是故汉高帝引兵至鲁。闻弦歌之声。诗又因弦歌而传。尤宜其无错谬者也。浮邱伯,大毛公皆同时受诗于荀卿。况浮邱伯秦时诸生。又如辕固生在汉武时。已九十馀。计其寿。上去焚经戊子。生已十六七岁。韩婴孝文时为博士。未知其生在何时。然要当去焚经时不远。是四家之学。或在焚经之前。或去焚经不远之时。当见孔氏之旧。而顾其为说。互相矛盾。不出于一者。岂非门户之见欤。经之盛衰。由人主所尚不同。而时俗所趍舍者异也。汉时诸儒多以经术为帝师而取卿相。蔡义以韩诗授昭帝。萧望之以齐诗为元帝傅。高嘉以鲁诗授元帝。而毛氏传独后出。至平帝时为王莽所习。得立学官。光武时仍之。后汉儒者郑众,贾徽,许慎之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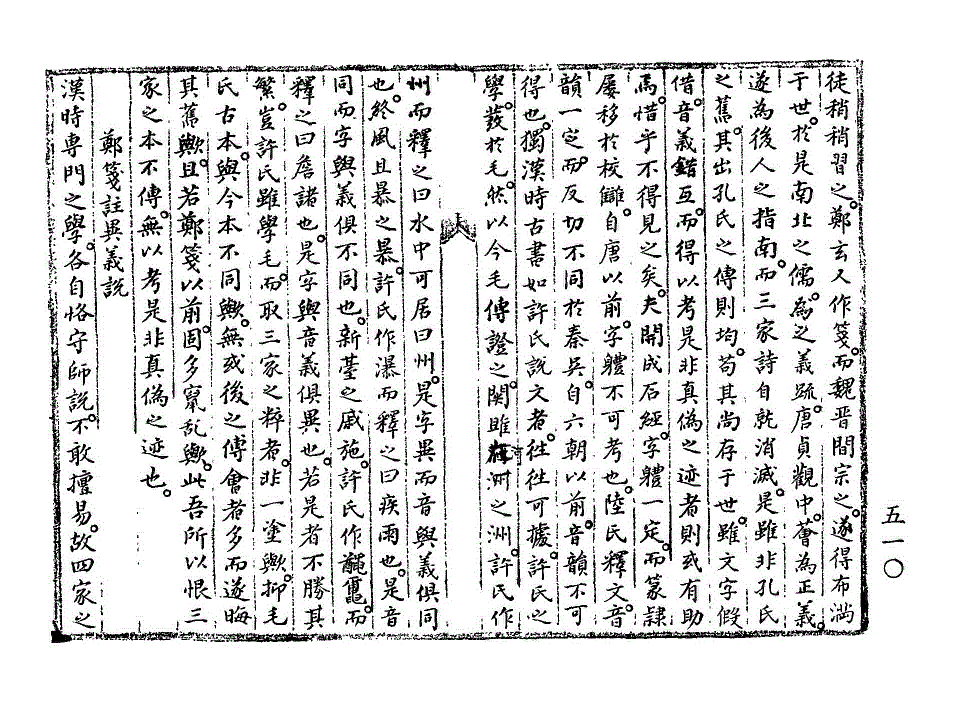 徒稍稍习之。郑玄又作笺。而魏晋间宗之。遂得布满于世。于是南北之儒。为之义疏。唐贞观中。荟为正义。遂为后人之指南。而三家诗自就消灭。是虽非孔氏之旧。其出孔氏之传则均。苟其尚存于世。虽文字假借。音义错互。而得以考是非真伪之迹者则或有助焉。惜乎不得见之矣。夫开成石经。字体一定。而篆隶屡移于校雠。自唐以前。字体不可考也。陆氏释文。音韵一定。而反切不同于秦吴。自六朝以前。音韵不可得也。独汉时古书如许氏说文者。往往可据。许氏之学。发于毛。然以今毛传證之。关雎在河之洲。许氏作州而释之曰水中可居曰州。是字异而音与义俱同也。终风且暴之暴。许氏作瀑而释之曰疾雨也。是音同而字与义俱不同也。新台之戚施。许氏作𪓰𪓿。而释之曰詹诸也。是字与音义俱异也。若是者不胜其繁。岂许氏虽学毛。而取三家之粹者。非一涂欤。抑毛氏古本。与今本不同欤。无或后之傅会者多而遂晦其旧欤。且若郑笺以前。固多窜乱欤。此吾所以恨三家之本不传。无以考是非真伪之迹也。
徒稍稍习之。郑玄又作笺。而魏晋间宗之。遂得布满于世。于是南北之儒。为之义疏。唐贞观中。荟为正义。遂为后人之指南。而三家诗自就消灭。是虽非孔氏之旧。其出孔氏之传则均。苟其尚存于世。虽文字假借。音义错互。而得以考是非真伪之迹者则或有助焉。惜乎不得见之矣。夫开成石经。字体一定。而篆隶屡移于校雠。自唐以前。字体不可考也。陆氏释文。音韵一定。而反切不同于秦吴。自六朝以前。音韵不可得也。独汉时古书如许氏说文者。往往可据。许氏之学。发于毛。然以今毛传證之。关雎在河之洲。许氏作州而释之曰水中可居曰州。是字异而音与义俱同也。终风且暴之暴。许氏作瀑而释之曰疾雨也。是音同而字与义俱不同也。新台之戚施。许氏作𪓰𪓿。而释之曰詹诸也。是字与音义俱异也。若是者不胜其繁。岂许氏虽学毛。而取三家之粹者。非一涂欤。抑毛氏古本。与今本不同欤。无或后之傅会者多而遂晦其旧欤。且若郑笺以前。固多窜乱欤。此吾所以恨三家之本不传。无以考是非真伪之迹也。郑笺注异义说
汉时专门之学。各自恪守师说。不敢擅易。故四家之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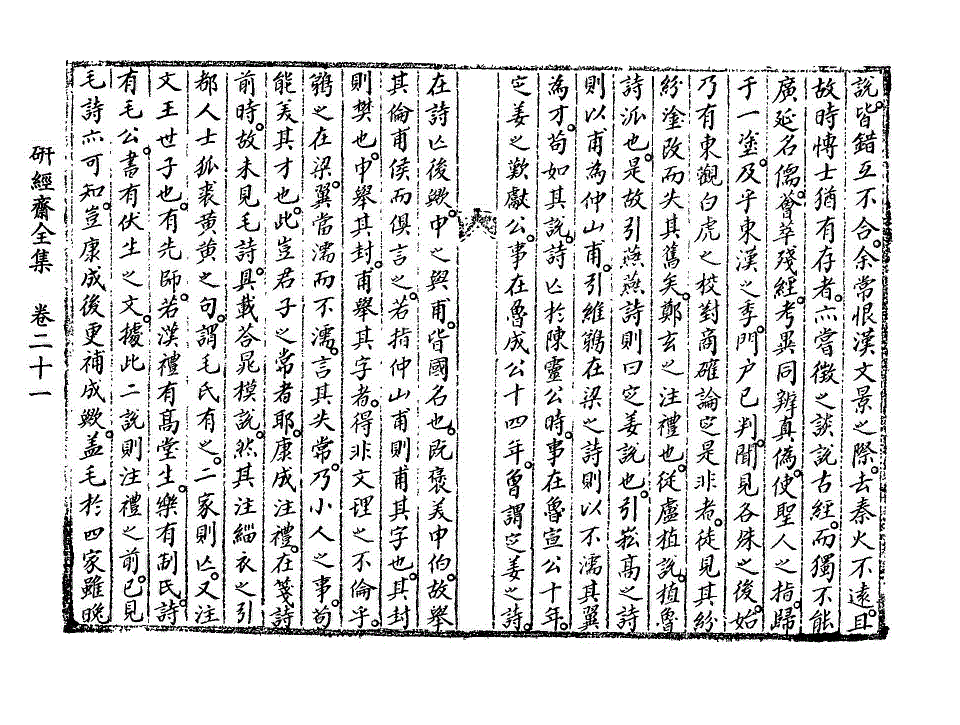 说。皆错互不合。余常恨汉文景之际。去秦火不远。且故时博士犹有存者。亦尝徵之谈说古经。而独不能广延名儒。荟萃残经。考异同辨真伪。使圣人之指。归于一涂。及乎东汉之季。门户已判。闻见各殊之后。始乃有东观白虎之校对商确论定是非者。徒见其纷纷涂改而失其旧矣。郑玄之注礼也。从卢植说。植鲁诗派也。是故引燕燕诗则曰定姜说也。引崧高之诗则以甫为仲山甫。引维鹈在梁之诗则以不濡其翼为才。苟如其说。诗亡于陈灵公时。事在鲁宣公十年。定姜之叹献公。事在鲁成公十四年。曾谓定姜之诗。在诗亡后欤。申之与甫。皆国名也。既褒美申伯。故举其伦甫侯而俱言之。若指仲山甫则甫其字也。其封则樊也。申举其封。甫举其字者。得非文理之不伦乎。鹈之在梁。翼当濡而不濡。言其失常。乃小人之事。苟能美其才也。此岂君子之常者耶。康成注礼。在笺诗前时。故未见毛诗。具载答晁模说。然其注缁衣之引都人士狐裘黄黄之句。谓毛氏有之。二家则亡。又注文王世子也。有先师。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之文。据此二说则注礼之前。已见毛诗亦可知。岂康成后更补成欤。盖毛于四家虽晚
说。皆错互不合。余常恨汉文景之际。去秦火不远。且故时博士犹有存者。亦尝徵之谈说古经。而独不能广延名儒。荟萃残经。考异同辨真伪。使圣人之指。归于一涂。及乎东汉之季。门户已判。闻见各殊之后。始乃有东观白虎之校对商确论定是非者。徒见其纷纷涂改而失其旧矣。郑玄之注礼也。从卢植说。植鲁诗派也。是故引燕燕诗则曰定姜说也。引崧高之诗则以甫为仲山甫。引维鹈在梁之诗则以不濡其翼为才。苟如其说。诗亡于陈灵公时。事在鲁宣公十年。定姜之叹献公。事在鲁成公十四年。曾谓定姜之诗。在诗亡后欤。申之与甫。皆国名也。既褒美申伯。故举其伦甫侯而俱言之。若指仲山甫则甫其字也。其封则樊也。申举其封。甫举其字者。得非文理之不伦乎。鹈之在梁。翼当濡而不濡。言其失常。乃小人之事。苟能美其才也。此岂君子之常者耶。康成注礼。在笺诗前时。故未见毛诗。具载答晁模说。然其注缁衣之引都人士狐裘黄黄之句。谓毛氏有之。二家则亡。又注文王世子也。有先师。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之文。据此二说则注礼之前。已见毛诗亦可知。岂康成后更补成欤。盖毛于四家虽晚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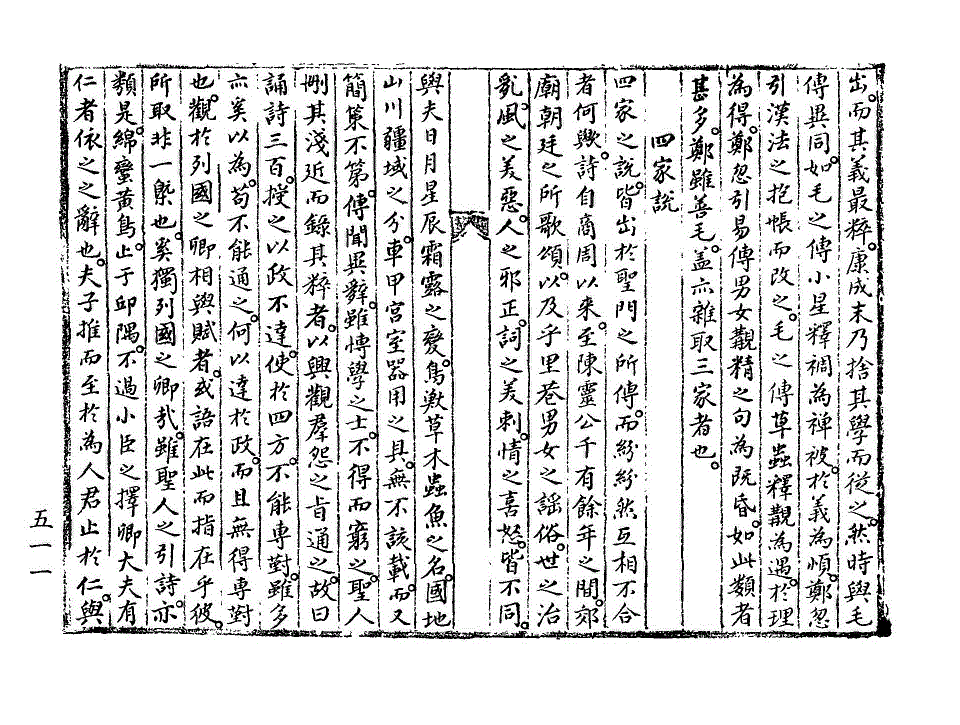 出。而其义最粹。康成末乃舍其学而从之。然时与毛传异同。如毛之传小星释裯为襌被。于义为㥧。郑忽引汉法之抱帐而改之。毛之传草虫释觏为遇。于理为得。郑忽引易传男女觏精之句为既昏。如此类者甚多。郑虽善毛。盖亦杂取三家者也。
出。而其义最粹。康成末乃舍其学而从之。然时与毛传异同。如毛之传小星释裯为襌被。于义为㥧。郑忽引汉法之抱帐而改之。毛之传草虫释觏为遇。于理为得。郑忽引易传男女觏精之句为既昏。如此类者甚多。郑虽善毛。盖亦杂取三家者也。四家说
四家之说。皆出于圣门之所传。而纷纷然互相不合者何欤。诗自商周以来。至陈灵公千有馀年之间。郊庙朝廷之所歌颂。以及乎里巷男女之谣俗。世之治乱。风之美恶。人之邪正。词之美刺。情之喜怒。皆不同。与夫日月星辰霜露之变。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国地山川疆域之分。车甲宫室器用之具。无不该载。而又简策不第。传闻异辞。虽博学之士。不得而穷之。圣人删其浅近而录其粹者。以兴观群怨之旨通之。故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苟不能通之。何以达于政。而且无得专对也。观于列国之卿相与赋者。或语在此而指在乎彼。所取非一槩也。奚独列国之卿哉。虽圣人之引诗。亦类是。绵蛮黄鸟。止于邱隅。不过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之辞也。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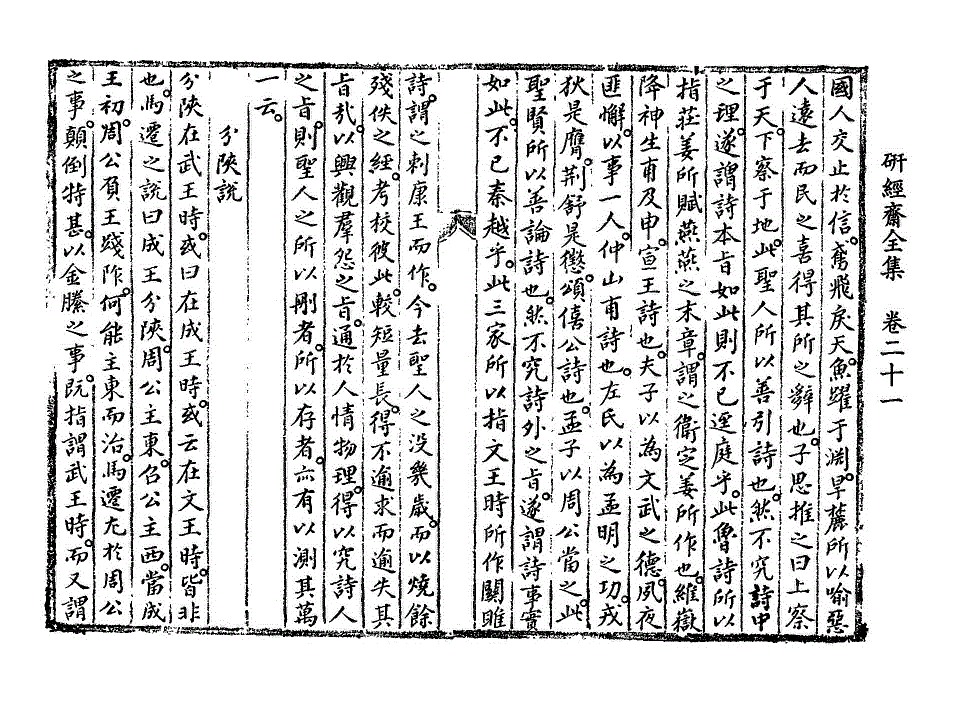 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所以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喜得其所之辞也。子思推之曰上察于天。下察于地。此圣人所以善引诗也。然不究诗中之理。遂谓诗本旨如此则不已径庭乎。此鲁诗所以指庄姜所赋燕燕之末章。谓之卫定姜所作也。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颂僖公诗也。孟子以周公当之。此圣贤所以善论诗也。然不究诗外之旨。遂谓诗事实如此。不已秦越乎。此三家所以指文王时所作关雎诗。谓之刺康王而作。今去圣人之没几岁。而以烧馀残佚之经。考校彼此。较短量长。得不逾求而逾失其旨哉。以兴观群怨之旨。通于人情物理。得以究诗人之旨。则圣人之所以删者。所以存者。亦有以测其万一云。
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所以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喜得其所之辞也。子思推之曰上察于天。下察于地。此圣人所以善引诗也。然不究诗中之理。遂谓诗本旨如此则不已径庭乎。此鲁诗所以指庄姜所赋燕燕之末章。谓之卫定姜所作也。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颂僖公诗也。孟子以周公当之。此圣贤所以善论诗也。然不究诗外之旨。遂谓诗事实如此。不已秦越乎。此三家所以指文王时所作关雎诗。谓之刺康王而作。今去圣人之没几岁。而以烧馀残佚之经。考校彼此。较短量长。得不逾求而逾失其旨哉。以兴观群怨之旨。通于人情物理。得以究诗人之旨。则圣人之所以删者。所以存者。亦有以测其万一云。分陕说
分陕在武王时。或曰在成王时。或云在文王时。皆非也。马迁之说曰成王分陕。周公主东。召公主西。当成王初。周公负王践阼。何能主东而治。马迁尤于周公之事。颠倒特甚。以金縢之事。既指谓武王时。而又谓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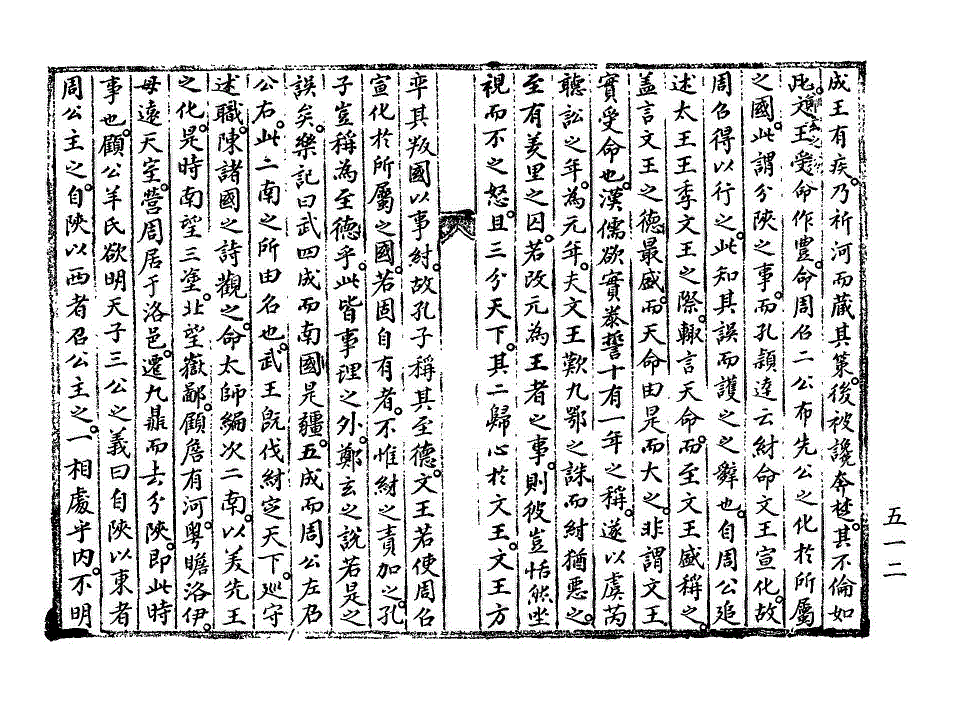 成王有疾。乃祈河而藏其策。后被谗奔楚。其不伦如此。郑玄之说文王受命作礼。命周召二公布先公之化于所属之国。此谓分陕之事。而孔颖达云纣命文王宣化。故周召得以行之。此知其误而护之之辞也。自周公追述太王王季文王之际。辄言天命。而至文王盛称之。盖言文王之德最盛。而天命由是而大之。非谓文王实受命也。汉儒欲实泰誓十有一年之称。遂以虞芮听讼之年。为元年。夫文王叹九鄂之诛而纣犹恶之。至有羑里之囚。若改元为王者之事。则彼岂恬然坐视而不之怒。且三分天下。其二归心于文王。文王方率其叛国以事纣。故孔子称其至德。文王若使周召宣化于所属之国。若固自有者。不惟纣之责加之。孔子岂称为至德乎。此皆事理之外。郑玄之说若是之误矣。乐记曰武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此二南之所由名也。武王既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诸国之诗观之。命太师编次二南。以美先王之化。是时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迁九鼎而去分陕。即此时事也。顾公羊氏欲明天子三公之义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不明
成王有疾。乃祈河而藏其策。后被谗奔楚。其不伦如此。郑玄之说文王受命作礼。命周召二公布先公之化于所属之国。此谓分陕之事。而孔颖达云纣命文王宣化。故周召得以行之。此知其误而护之之辞也。自周公追述太王王季文王之际。辄言天命。而至文王盛称之。盖言文王之德最盛。而天命由是而大之。非谓文王实受命也。汉儒欲实泰誓十有一年之称。遂以虞芮听讼之年。为元年。夫文王叹九鄂之诛而纣犹恶之。至有羑里之囚。若改元为王者之事。则彼岂恬然坐视而不之怒。且三分天下。其二归心于文王。文王方率其叛国以事纣。故孔子称其至德。文王若使周召宣化于所属之国。若固自有者。不惟纣之责加之。孔子岂称为至德乎。此皆事理之外。郑玄之说若是之误矣。乐记曰武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此二南之所由名也。武王既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诸国之诗观之。命太师编次二南。以美先王之化。是时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迁九鼎而去分陕。即此时事也。顾公羊氏欲明天子三公之义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不明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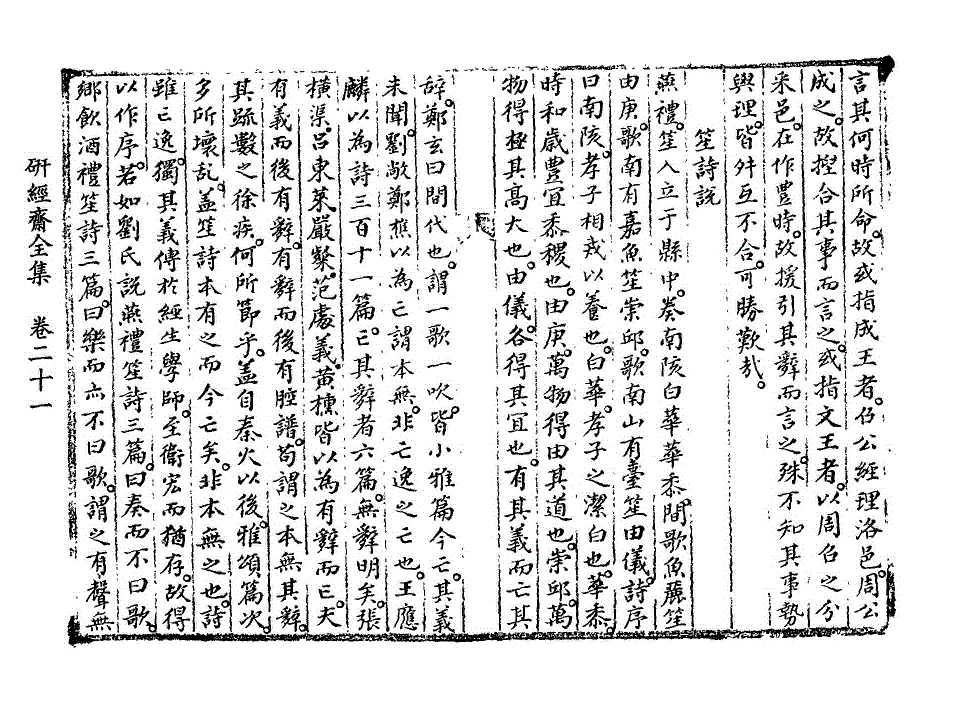 言其何时所命。故或指成王者。召公经理洛邑。周公成之。故捏合其事而言之。或指文王者。以周召之分采邑。在作礼时。故援引其辞而言之。殊不知其事势与理。皆舛互不合。可胜叹哉。
言其何时所命。故或指成王者。召公经理洛邑。周公成之。故捏合其事而言之。或指文王者。以周召之分采邑。在作礼时。故援引其辞而言之。殊不知其事势与理。皆舛互不合。可胜叹哉。笙诗说
燕礼。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诗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礼宜黍稷也。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邱。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玄曰间代也。谓一歌一吹。皆小雅篇今亡。其义未闻。刘敞郑樵以为亡谓本无。非亡逸之亡也。王应麟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亡其辞者六篇。无辞明矣。张横渠,吕东莱,严粲,范处义,黄櫄皆以为有辞而亡。夫有义而后有辞。有辞而后有腔谱。苟谓之本无其辞。其疏数之徐疾。何所节乎。盖自秦火以后。雅颂篇次。多所坏乱。盖笙诗本有之而今亡矣。非本无之也。诗虽亡逸。独其义传于经生学师。至卫宏而犹存。故得以作序。若如刘氏说燕礼笙诗三篇。曰奏而不曰歌。乡饮酒礼笙诗三篇。曰乐而亦不曰歌。谓之有声无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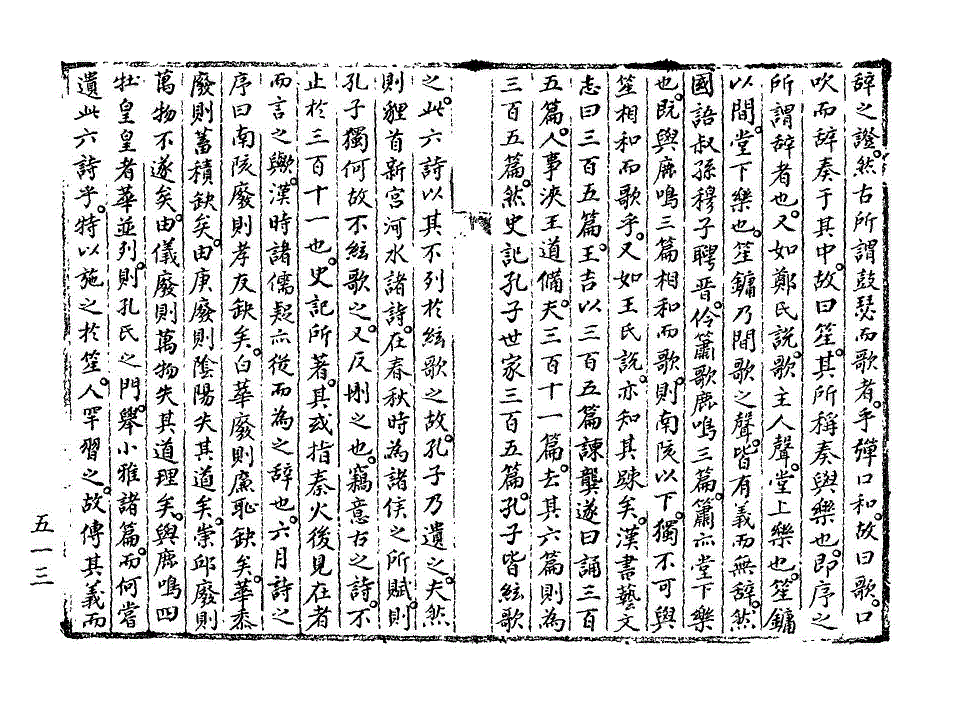 辞之證。然古所谓鼓瑟而歌者。手弹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辞奏于其中。故曰笙。其所称奏与乐也。即序之所谓辞者也。又如郑氏说。歌主人声。堂上乐也。笙镛以间。堂下乐也。笙镛乃间歌之声。皆有义而无辞。然国语叔孙穆子聘晋。伶箫歌鹿鸣三篇。箫亦堂下乐也。既与鹿鸣三篇相和而歌。则南陔以下。独不可与笙相和而歌乎。又如王氏说。亦知其疏矣。汉书艺文志曰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谏龚遂曰诵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夫三百十一篇。去其六篇则为三百五篇。然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六诗以其不列于弦歌之故。孔子乃遗之。夫然则狸首新宫河水诸诗。在春秋时为诸侯之所赋。则孔子独何故不弦歌之。又反删之也。窃意古之诗。不止于三百十一也。史记所著。其或指秦火后见在者而言之欤。汉时诸儒疑亦从而为之辞也。六月诗之序曰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矣。崇邱废则万物不遂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与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并列。则孔氏之门。举小雅诸篇。而何尝遗此六诗乎。特以施之于笙。人罕习之。故传其义而
辞之證。然古所谓鼓瑟而歌者。手弹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辞奏于其中。故曰笙。其所称奏与乐也。即序之所谓辞者也。又如郑氏说。歌主人声。堂上乐也。笙镛以间。堂下乐也。笙镛乃间歌之声。皆有义而无辞。然国语叔孙穆子聘晋。伶箫歌鹿鸣三篇。箫亦堂下乐也。既与鹿鸣三篇相和而歌。则南陔以下。独不可与笙相和而歌乎。又如王氏说。亦知其疏矣。汉书艺文志曰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谏龚遂曰诵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夫三百十一篇。去其六篇则为三百五篇。然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六诗以其不列于弦歌之故。孔子乃遗之。夫然则狸首新宫河水诸诗。在春秋时为诸侯之所赋。则孔子独何故不弦歌之。又反删之也。窃意古之诗。不止于三百十一也。史记所著。其或指秦火后见在者而言之欤。汉时诸儒疑亦从而为之辞也。六月诗之序曰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矣。崇邱废则万物不遂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与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并列。则孔氏之门。举小雅诸篇。而何尝遗此六诗乎。特以施之于笙。人罕习之。故传其义而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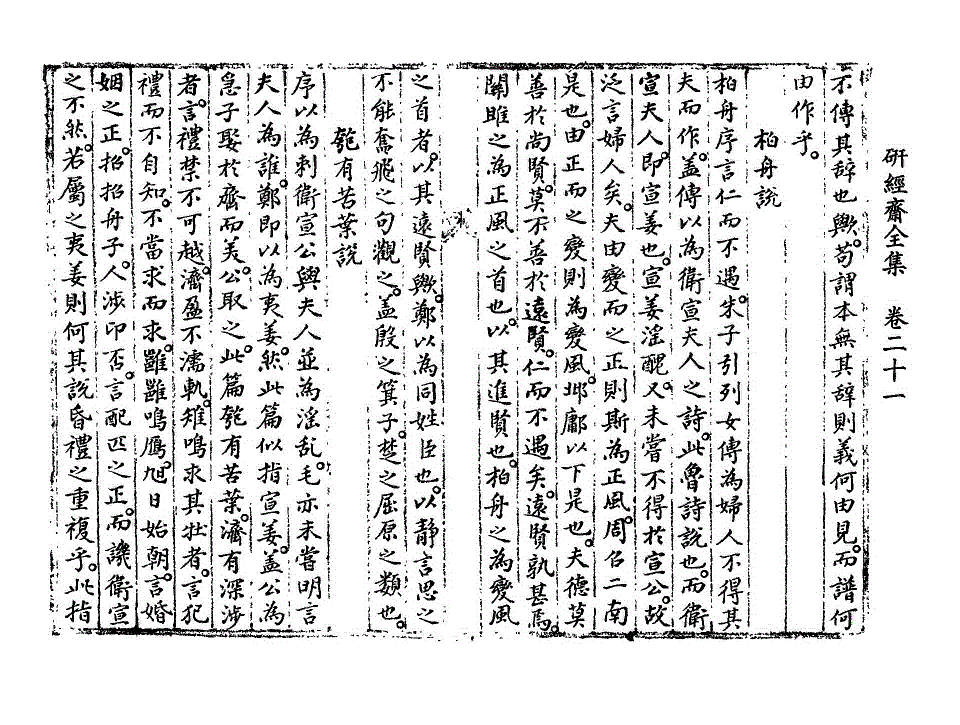 不传其辞也欤。苟谓本无其辞则义何由见。而谱何由作乎。
不传其辞也欤。苟谓本无其辞则义何由见。而谱何由作乎。柏舟说
柏舟序言仁而不遇。朱子引列女传为妇人不得其夫而作。盖传以为卫宣夫人之诗。此鲁诗说也。而卫宣夫人。即宣姜也。宣姜淫丑。又未尝不得于宣公。故泛言妇人矣。夫由变而之正则斯为正风。周召二南是也。由正而之变则为变风。邶鄘以下是也。夫德莫善于尚贤。莫不善于远贤。仁而不遇矣。远贤孰甚焉。关雎之为正风之首也。以其进贤也。柏舟之为变风之首者。以其远贤欤。郑以为同姓臣也。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之句观之。盖殷之箕子。楚之屈原之类也。
匏有苦叶说
序以为刺卫宣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亦未尝明言夫人为谁。郑即以为夷姜。然此篇似指宣姜。盖公为急子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此篇匏有苦叶。济有深涉者。言礼禁不可越。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者。言犯礼而不自知。不当求而求。雍雍鸣雁。旭日始朝。言婚姻之正。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言配匹之正。而讥卫宣之不然。若属之夷姜则何其说昏礼之重复乎。此指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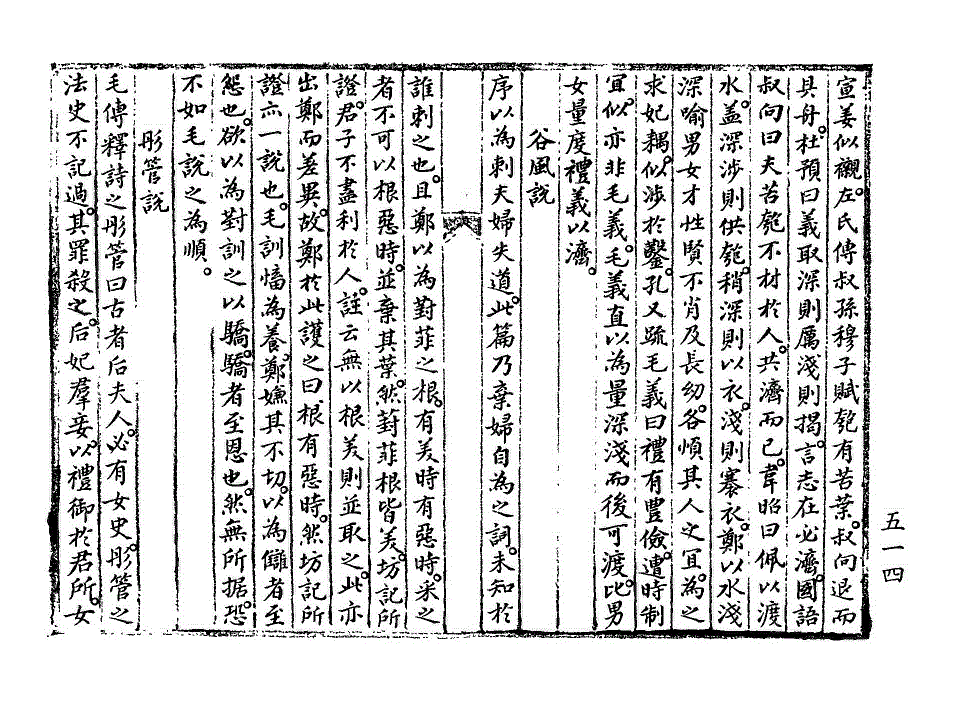 宣姜似衬。左氏传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杜预曰义取深则厉浅则揭。言志在必济。国语叔向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韦昭曰佩以渡水。盖深涉则供匏。稍深则以衣。浅则褰衣。郑以水浅深喻男女才性贤不肖及长幼。各㥧其人之宜。为之求妃耦。似涉于凿。孔又疏毛义曰礼有礼俭。遭时制宜。似亦非毛义。毛义直以为量深浅而后可渡。比男女量度礼义以济。
宣姜似衬。左氏传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杜预曰义取深则厉浅则揭。言志在必济。国语叔向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韦昭曰佩以渡水。盖深涉则供匏。稍深则以衣。浅则褰衣。郑以水浅深喻男女才性贤不肖及长幼。各㥧其人之宜。为之求妃耦。似涉于凿。孔又疏毛义曰礼有礼俭。遭时制宜。似亦非毛义。毛义直以为量深浅而后可渡。比男女量度礼义以济。谷风说
序以为刺夫妇失道。此篇乃弃妇自为之词。未知于谁刺之也。且郑以为葑菲之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然葑菲根皆美。坊记所證。君子不尽利于人。注云无以根美则并取之。此亦出郑而差异。故郑于此护之曰根有恶时。然坊记所證亦一说也。毛训慉为养。郑嫌其不切。以为雠者至怨也。欲以为对训之以骄。骄者至恩也。然无所据。恐不如毛说之为顺。
彤管说
毛传释诗之彤管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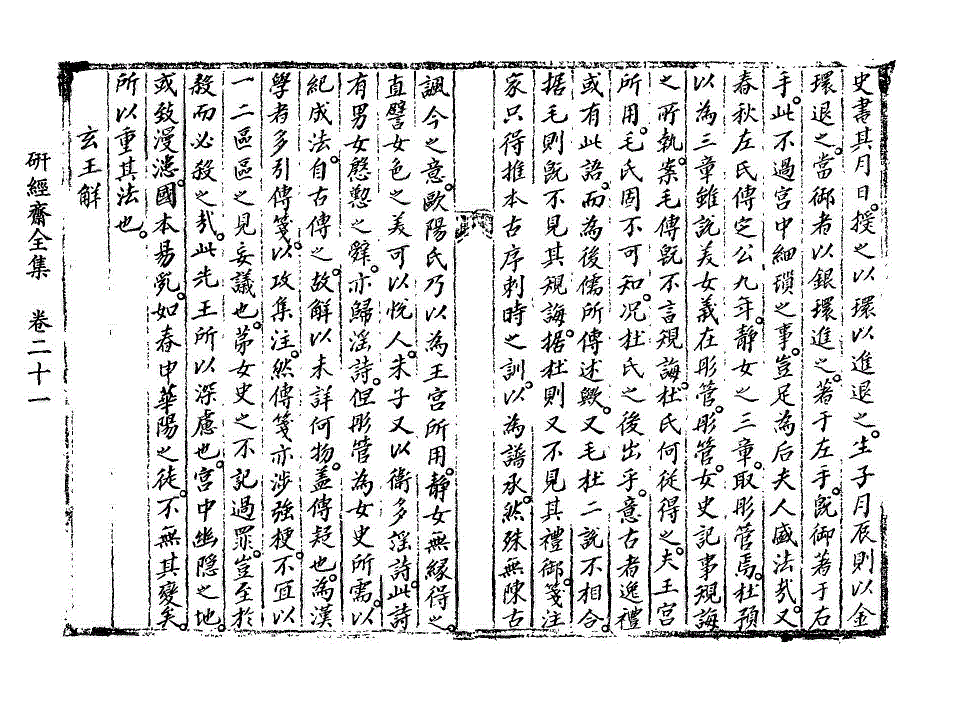 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此不过宫中细琐之事。岂足为后夫人盛法哉。又春秋左氏传定公九年。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预以为三章虽说美女义在彤管。彤管。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案毛传既不言规诲。杜氏何从得之。夫王宫所用。毛氏固不可知。况杜氏之后出乎。意古者逸礼或有此语。而为后儒所传述欤。又毛杜二说不相合。据毛则既不见其规诲。据杜则又不见其礼御。笺注家只得推本古序刺时之训。以为谱承。然殊无陈古讽今之意。欧阳氏乃以为王宫所用。静女无缘得之。直譬女色之美可以悦人。朱子又以卫多淫诗。此诗有男女慇勤之辞。亦归淫诗。但彤管为女史所需。以纪成法。自古传之。故解以未详何物。盖传疑也。为汉学者多引传笺。以攻集注。然传笺亦涉强梗。不宜以一二区区之见妄议也。第女史之不记过罪。岂至于杀而必杀之哉。此先王所以深虑也。宫中幽隐之地。或致漫漶。国本易乱。如春申华阳之徒。不无其变矣。所以重其法也。
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此不过宫中细琐之事。岂足为后夫人盛法哉。又春秋左氏传定公九年。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预以为三章虽说美女义在彤管。彤管。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案毛传既不言规诲。杜氏何从得之。夫王宫所用。毛氏固不可知。况杜氏之后出乎。意古者逸礼或有此语。而为后儒所传述欤。又毛杜二说不相合。据毛则既不见其规诲。据杜则又不见其礼御。笺注家只得推本古序刺时之训。以为谱承。然殊无陈古讽今之意。欧阳氏乃以为王宫所用。静女无缘得之。直譬女色之美可以悦人。朱子又以卫多淫诗。此诗有男女慇勤之辞。亦归淫诗。但彤管为女史所需。以纪成法。自古传之。故解以未详何物。盖传疑也。为汉学者多引传笺。以攻集注。然传笺亦涉强梗。不宜以一二区区之见妄议也。第女史之不记过罪。岂至于杀而必杀之哉。此先王所以深虑也。宫中幽隐之地。或致漫漶。国本易乱。如春申华阳之徒。不无其变矣。所以重其法也。玄王解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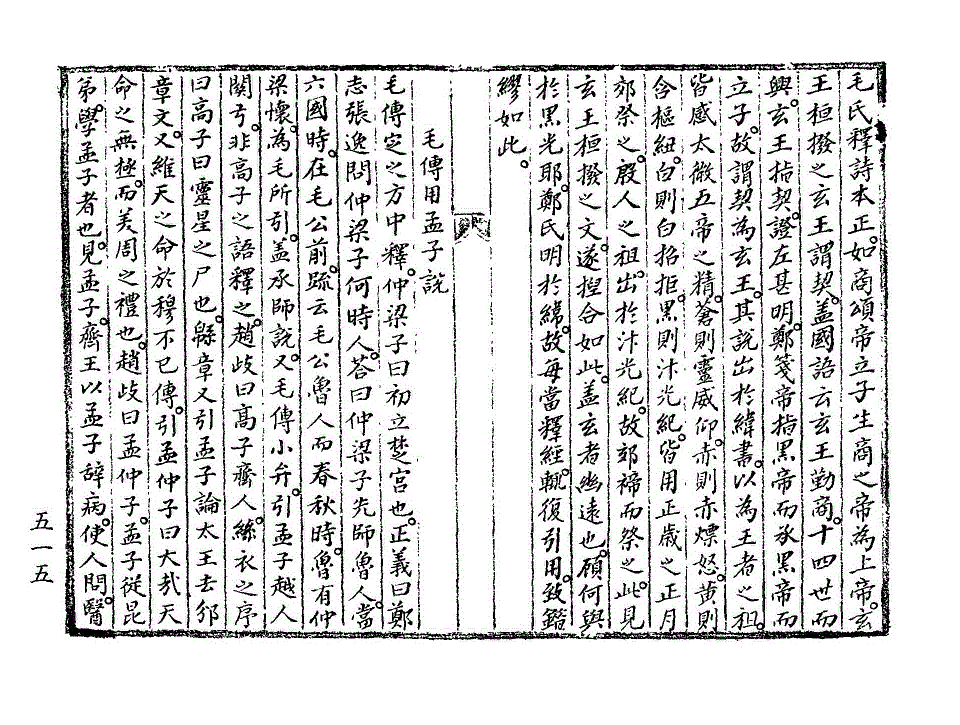 毛氏释诗本正。如商颂帝立子生商之帝为上帝。玄王桓拨之玄王谓契。盖国语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玄王指契。證左甚明。郑笺帝指黑帝而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其说出于纬书。以为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殷人之祖。出于汁光纪。故郊禘而祭之。此见玄王桓拨之文。遂捏合如此。盖玄者幽远也。顾何与于黑光耶。郑氏明于纬。故每当释经。辄复引用。致错缪如此。
毛氏释诗本正。如商颂帝立子生商之帝为上帝。玄王桓拨之玄王谓契。盖国语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玄王指契。證左甚明。郑笺帝指黑帝而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其说出于纬书。以为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殷人之祖。出于汁光纪。故郊禘而祭之。此见玄王桓拨之文。遂捏合如此。盖玄者幽远也。顾何与于黑光耶。郑氏明于纬。故每当释经。辄复引用。致错缪如此。毛传用孟子说
毛传定之方中释。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正义曰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疏云毛公鲁人而春秋时。鲁有仲梁怀。为毛所引。盖承师说。又毛传小弁。引孟子越人关弓。非高子之语释之。赵歧曰高子齐人。丝衣之序曰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绵章又引孟子论太王去邠章文。又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赵歧曰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孟子者也。见孟子。齐王以孟子辞病。使人问。医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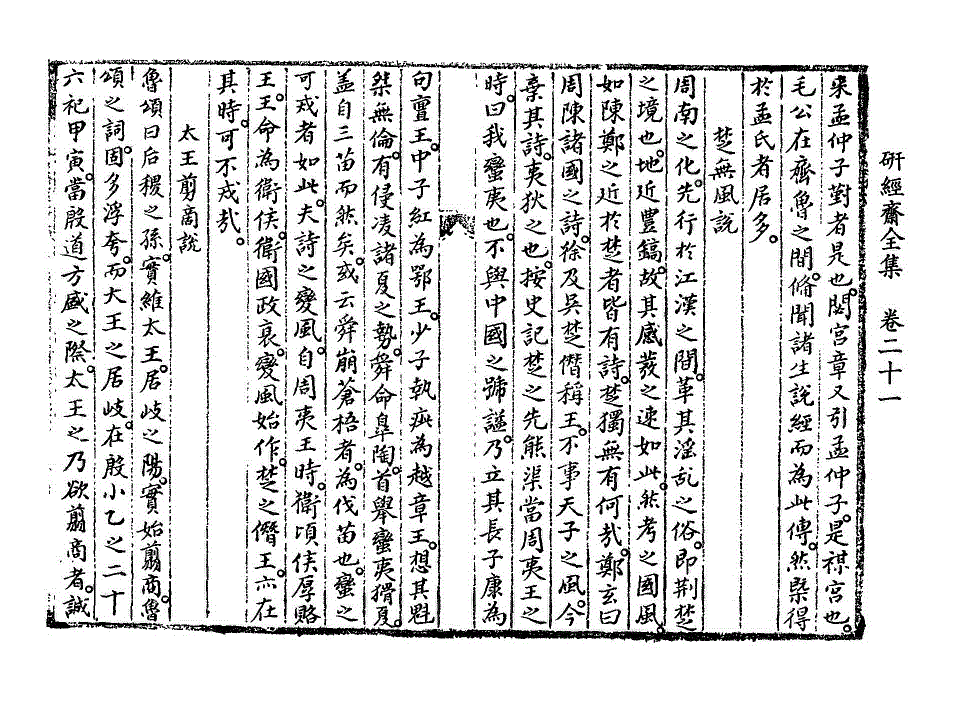 来孟仲子对者是也。閟宫章又引孟仲子。是禖宫也。毛公在齐鲁之间。备闻诸生说经而为此传。然槩得于孟氏者居多。
来孟仲子对者是也。閟宫章又引孟仲子。是禖宫也。毛公在齐鲁之间。备闻诸生说经而为此传。然槩得于孟氏者居多。楚无风说
周南之化。先行于江汉之间。革其淫乱之俗。即荆楚之境也。地近礼镐。故其感发之速如此。然考之国风。如陈郑之近于楚者皆有诗。楚独无有何哉。郑玄曰周陈诸国之诗。徐及吴楚僭称王。不事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按史记楚之先熊渠当周夷王之时。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想其魁桀无伦。有侵凌诸夏之势。舜命皋陶。首举蛮夷猾夏。盖自三苗而然矣。或云舜崩苍梧者。为伐苗也。蛮之可戒者如此。夫诗之变风。自周夷王时。卫顷侯厚赂王。王命为卫侯。卫国政衰。变风始作。楚之僭王。亦在其时。可不戒哉。
太王剪商说
鲁颂曰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鲁颂之词。固多浮夸。而大王之居岐。在殷小乙之二十六祀甲寅。当殷道方盛之际。太王之乃欲剪商者。诚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6L 页
 不究解其理。故先儒乃以为王业始著。盖有剪商之渐。非谓大王实有其志。大王顾生长西陲。草昧灵智。见文王之德于孩提之中。知其世当兴。乃欲立季历而传之。此岂雍容守义分者哉。且观其迁岐也。疆理室家之制。已有王居之气像。与陶复居邠时大异。此其志不欲止西方诸侯之列者亦明矣。盖其洞达来许知殷祚必丧。积仁累功。欲以兴王。亦无足怪也。大王盖奇伟神异人也。苟律之以禹汤学知之圣则诚失之矣。
不究解其理。故先儒乃以为王业始著。盖有剪商之渐。非谓大王实有其志。大王顾生长西陲。草昧灵智。见文王之德于孩提之中。知其世当兴。乃欲立季历而传之。此岂雍容守义分者哉。且观其迁岐也。疆理室家之制。已有王居之气像。与陶复居邠时大异。此其志不欲止西方诸侯之列者亦明矣。盖其洞达来许知殷祚必丧。积仁累功。欲以兴王。亦无足怪也。大王盖奇伟神异人也。苟律之以禹汤学知之圣则诚失之矣。诗三纬说
三纬者。赋比兴也。正义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康成云铺陈善恶则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苟如正义则赋固易见而比兴错出。比专于恶。兴专于善。其蔽也偏。夫一篇之中。或具赋体。或具兴体。或具比体。盖三纬不具则无以为诗。譬之文绣红而无绿。黑而无白。焉能错综为文乎。朱子曰赋者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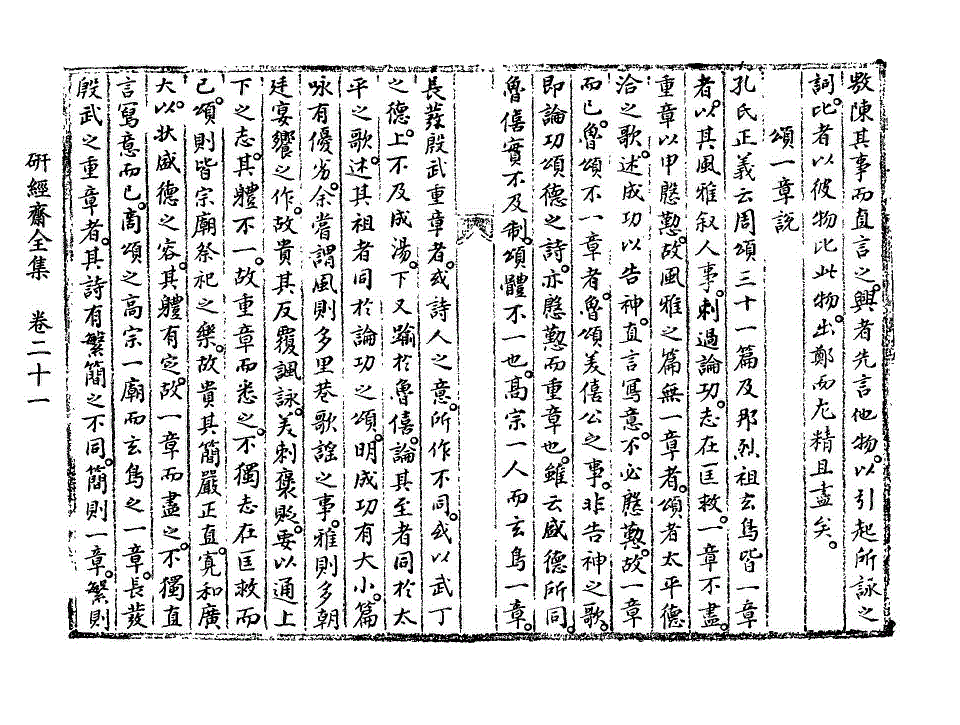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出郑而尤精且尽矣。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出郑而尤精且尽矣。颂一章说
孔氏正义云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慇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意。不必慇勤。故一章而已。鲁颂不一章者。鲁颂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即论功颂德之诗。亦慇勤而重章也。虽云盛德所同。鲁僖实不及制。颂体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鸟一章。长发殷武重章者。或诗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汤。下又踰于鲁僖。论其至者同于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于论功之颂。明成功有大小。篇咏有优劣。余尝谓风则多里巷歌谣之事。雅则多朝廷宴飨之作。故贵其反覆讽咏。美刺褒贬。要以通上下之志。其体不一。故重章而悉之。不独志在匡救而已。颂则皆宗庙祭祀之乐。故贵其简严正直。宽和广大。以状盛德之容。其体有定。故一章而尽之。不独直言写意而已。商颂之高宗一庙而玄鸟之一章。长发殷武之重章者。其诗有繁简之不同。简则一章。繁则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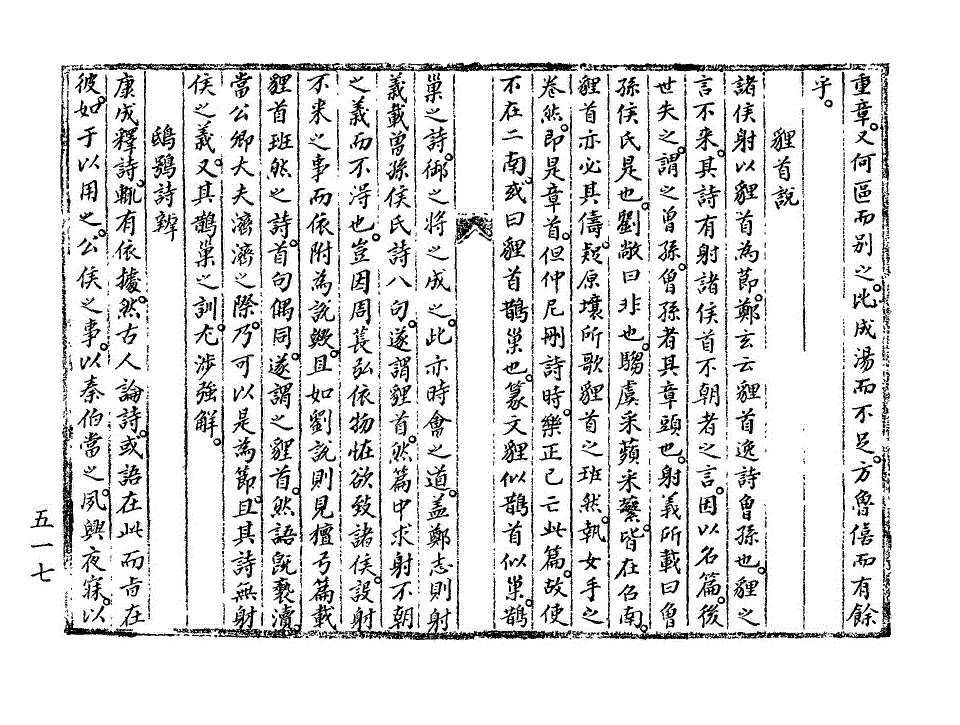 重章。又何区而别之。比成汤而不足。方鲁僖而有馀乎。
重章。又何区而别之。比成汤而不足。方鲁僖而有馀乎。狸首说
诸侯射以狸首为节。郑玄云狸首逸诗曾孙也。狸之言不来。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曾孙者其章头也。射义所载曰曾孙侯氏是也。刘敞曰非也。驺虞采蘋采蘩。皆在召南。狸首亦必其俦。疑原壤所歌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即是章首。但仲尼删诗时。乐正已亡此篇。故使不在二南。或曰狸首鹊巢也。篆文狸似鹊首似巢。鹊巢之诗。御之将之成之。此亦时会之道。盖郑志则射义载曾孙侯氏诗八句。遂谓狸首。然篇中求射不朝之义而不得也。岂因周苌弘依物怪欲致诸侯。设射不来之事而依附为说欤。且如刘说则见檀弓篇载狸首班然之诗。首句偶同。遂谓之狸首。然语既亵渎。当公卿大夫济济之际。乃可以是为节。且其诗无射侯之义。又其鹊巢之训。尤涉强解。
鸱鸮诗辨
康成释诗。辄有依据。然古人论诗。或语在此而旨在彼。如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以秦伯当之。夙兴夜寐。以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8H 页
 事一人。以孟明蔽之。诒厥孙谟。以燕翼子。以子桑盖之则可乎。康成之释。多此类也。是故引左传怨耦曰仇。以解关雎之好逑。引左传能官人之言。以解卷耳之周行。虽有考据。其本旨果出此否。至鸱鸮诗。以金縢篇有居东二年。罪人斯得。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之文。以为成王因周公之出奔。治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其说何其曲也。周公之居摄。即商之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之法也。安有属党而为之与闻。且谓周公只爱护属党。而不念王室之艰者。岂周公之意乎。毛传本善。以子属之管蔡。意精而指正。郑乃以子属之成王。尤觉乖缪。倘非朱子集传之明有从违。后人得不迷方向乎。于此知朱子之功矣。
事一人。以孟明蔽之。诒厥孙谟。以燕翼子。以子桑盖之则可乎。康成之释。多此类也。是故引左传怨耦曰仇。以解关雎之好逑。引左传能官人之言。以解卷耳之周行。虽有考据。其本旨果出此否。至鸱鸮诗。以金縢篇有居东二年。罪人斯得。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之文。以为成王因周公之出奔。治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其说何其曲也。周公之居摄。即商之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之法也。安有属党而为之与闻。且谓周公只爱护属党。而不念王室之艰者。岂周公之意乎。毛传本善。以子属之管蔡。意精而指正。郑乃以子属之成王。尤觉乖缪。倘非朱子集传之明有从违。后人得不迷方向乎。于此知朱子之功矣。素冠辨
诗之桧风素冠章曰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毛传曰素冠练冠也。郑笺以为既祥之冠也。孔颖达曰郑以为练冠者。练布为之。经传之言素者。皆谓曰绢。未有以布为素者。知素冠非练。故易传以素冠为既祥之冠。王肃,孙毓以笺说为长。案檀弓说既练之服云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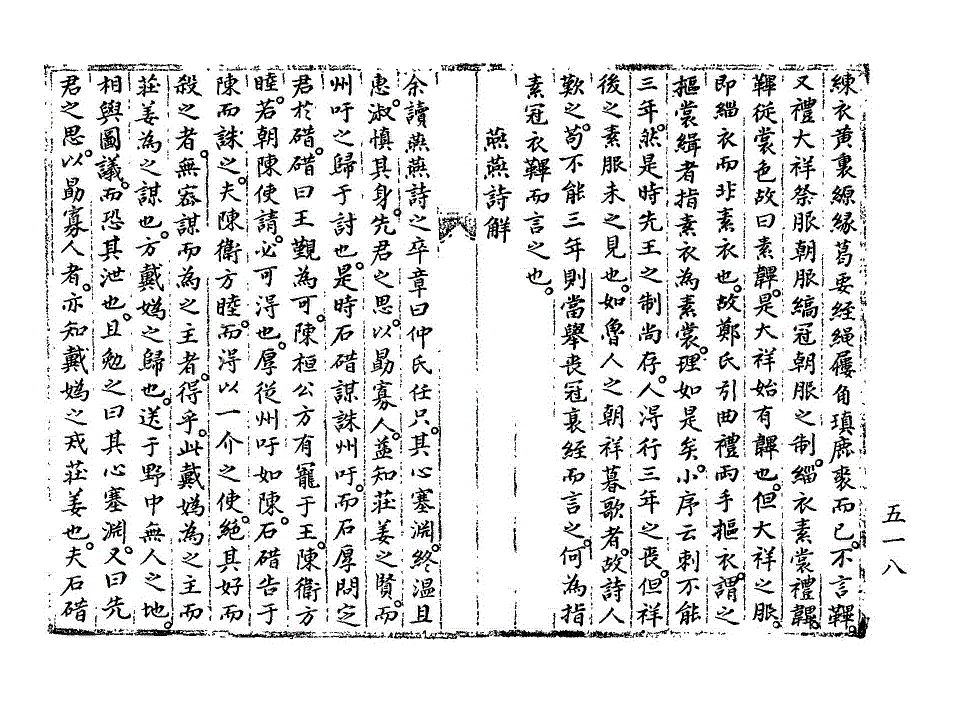 练衣黄里縓缘葛要绖绳屦角瑱鹿裘而已。不言鞸。又礼大祥祭服朝服缟冠朝服之制。缁衣素裳礼韠。鞸从裳色故曰素韠。是大祥始有韠也。但大祥之服。即缁衣而非素衣也。故郑氏引曲礼两手抠衣。谓之抠裳缉者指素衣为素裳。理如是矣。小序云刺不能三年。然是时先王之制尚存。人得行三年之丧。但祥后之素服未之见也。如鲁人之朝祥暮歌者。故诗人叹之。苟不能三年则当举丧冠衰绖而言之。何为指素冠衣鞸而言之也。
练衣黄里縓缘葛要绖绳屦角瑱鹿裘而已。不言鞸。又礼大祥祭服朝服缟冠朝服之制。缁衣素裳礼韠。鞸从裳色故曰素韠。是大祥始有韠也。但大祥之服。即缁衣而非素衣也。故郑氏引曲礼两手抠衣。谓之抠裳缉者指素衣为素裳。理如是矣。小序云刺不能三年。然是时先王之制尚存。人得行三年之丧。但祥后之素服未之见也。如鲁人之朝祥暮歌者。故诗人叹之。苟不能三年则当举丧冠衰绖而言之。何为指素冠衣鞸而言之也。燕燕诗解
余读燕燕诗之卒章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益知庄姜之贤。而州吁之归于讨也。是时石碏谋诛州吁。而石厚问定君于碏。碏曰王觐为可。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告于陈而诛之。夫陈卫方睦。而得以一介之使。绝其好而杀之者。无密谋而为之主者。得乎。此戴妫为之主而庄姜为之谋也。方戴妫之归也。送于野中无人之地。相与图议。而恐其泄也。且勉之曰其心塞渊。又曰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者。亦知戴妫之戒庄姜也。夫石碏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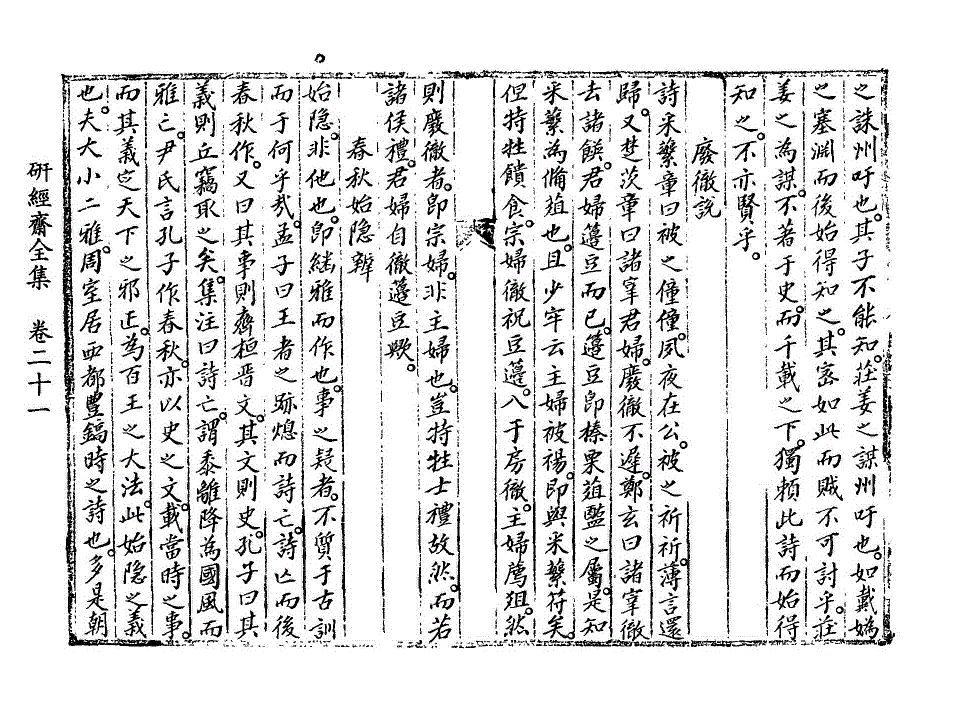 之诛州吁也。其子不能知。庄姜之谋州吁也。如戴妫之塞渊而后始得知之。其密如此而贼不可讨乎。庄姜之为谋。不著于史。而千载之下。独赖此诗而始得知之。不亦贤乎。
之诛州吁也。其子不能知。庄姜之谋州吁也。如戴妫之塞渊而后始得知之。其密如此而贼不可讨乎。庄姜之为谋。不著于史。而千载之下。独赖此诗而始得知之。不亦贤乎。废彻说
诗采蘩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还归。又楚茨章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郑玄曰诸宰彻去诸馔。君妇笾豆而已。笾豆即榛栗菹醢之属。是知采蘩为备菹也。且少牢云主妇被裼。即与采蘩符矣。但特牲馈食。宗妇彻祝豆笾。入于房彻。主妇荐俎。然则废彻者。即宗妇。非主妇也。岂特牲士礼故然。而若诸侯礼。君妇自彻笾豆欤。
春秋始隐辨
始隐。非他也。即继雅而作也。事之疑者。不质于古训而于何乎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又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集注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尹氏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而其义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始隐之义也。夫大小二雅。周室居西都礼镐时之诗也。多是朝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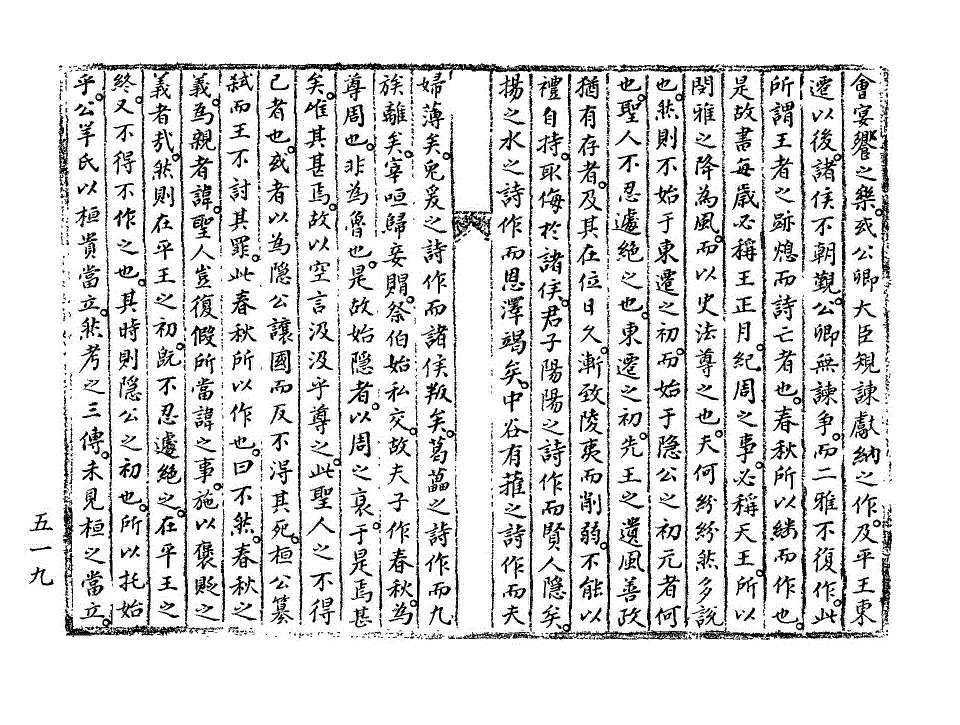 会宴飨之乐。或公卿大臣规谏献纳之作。及平王东迁以后。诸侯不朝觐。公卿无谏争。而二雅不复作。此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者也。春秋所以继而作也。是故书每岁必称王正月。纪周之事。必称天王。所以闵雅之降为风。而以史法尊之也。夫何纷纷然多说也。然则不始于东迁之初。而始于隐公之初元者何也。圣人不忍遽绝之也。东迁之初。先王之遗风善政犹有存者。及其在位日久。渐致陵夷而削弱。不能以礼自持。取侮于诸侯。君子阳阳之诗作而贤人隐矣。扬之水之诗作而恩泽竭矣。中谷有蓷之诗作而夫妇薄矣。兔爰之诗作而诸侯叛矣。葛藟之诗作而九族离矣。宰咺归妾赗。祭伯始私交。故夫子作春秋。为尊周也。非为鲁也。是故始隐者。以周之衰。于是焉甚矣。唯其甚焉。故以空言汲汲乎尊之。此圣人之不得已者也。或者以为隐公让国而反不得其死。桓公篡弑而王不讨其罪。此春秋所以作也。曰不然。春秋之义。为亲者讳。圣人岂复假所当讳之事。施以褒贬之义者哉。然则在平王之初。既不忍遽绝之。在平王之终。又不得不作之也。其时则隐公之初也。所以托始乎。公羊氏以桓贵当立。然考之三传。未见桓之当立。
会宴飨之乐。或公卿大臣规谏献纳之作。及平王东迁以后。诸侯不朝觐。公卿无谏争。而二雅不复作。此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者也。春秋所以继而作也。是故书每岁必称王正月。纪周之事。必称天王。所以闵雅之降为风。而以史法尊之也。夫何纷纷然多说也。然则不始于东迁之初。而始于隐公之初元者何也。圣人不忍遽绝之也。东迁之初。先王之遗风善政犹有存者。及其在位日久。渐致陵夷而削弱。不能以礼自持。取侮于诸侯。君子阳阳之诗作而贤人隐矣。扬之水之诗作而恩泽竭矣。中谷有蓷之诗作而夫妇薄矣。兔爰之诗作而诸侯叛矣。葛藟之诗作而九族离矣。宰咺归妾赗。祭伯始私交。故夫子作春秋。为尊周也。非为鲁也。是故始隐者。以周之衰。于是焉甚矣。唯其甚焉。故以空言汲汲乎尊之。此圣人之不得已者也。或者以为隐公让国而反不得其死。桓公篡弑而王不讨其罪。此春秋所以作也。曰不然。春秋之义。为亲者讳。圣人岂复假所当讳之事。施以褒贬之义者哉。然则在平王之初。既不忍遽绝之。在平王之终。又不得不作之也。其时则隐公之初也。所以托始乎。公羊氏以桓贵当立。然考之三传。未见桓之当立。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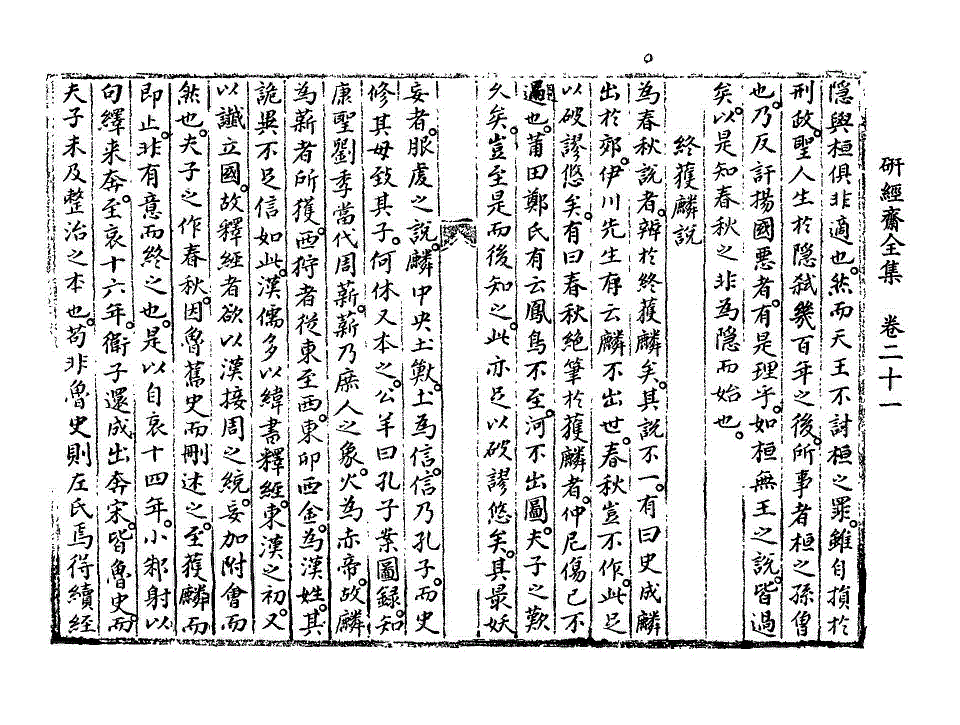 隐与桓俱非适也。然而天王不讨桓之罪。虽自损于刑政。圣人生于隐弑几百年之后。所事者桓之孙曾也。乃反讦扬国恶者。有是理乎。如桓无王之说。皆过矣。以是知春秋之非为隐而始也。
隐与桓俱非适也。然而天王不讨桓之罪。虽自损于刑政。圣人生于隐弑几百年之后。所事者桓之孙曾也。乃反讦扬国恶者。有是理乎。如桓无王之说。皆过矣。以是知春秋之非为隐而始也。终获麟说
为春秋说者。辨于终获麟矣。其说不一。有曰史成麟出于郊。伊川先生有云麟不出世。春秋岂不作。此足以破谬悠矣。有曰春秋绝笔于获麟者。仲尼伤己不遇也。莆田郑氏有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夫子之叹久矣。岂至是而后知之。此亦足以破谬悠矣。其最妖妄者。服虔之说。麟中央土兽。土为信。信乃孔子。而史修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公羊曰孔子案图录。知康圣刘季当代周薪。薪乃庶人之象。火为赤帝。故麟为薪者所获。西狩者从东至西。东卯西金。为汉姓。其诡异不足信如此。汉儒多以纬书释经。东汉之初。又以谶立国。故释经者欲以汉接周之统。妄加附会而然也。夫子之作春秋。因鲁旧史而删述之。至获麟而即止。非有意而终之也。是以自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至哀十六年。卫子还成出奔宋。皆鲁史。而夫子未及整治之本也。苟非鲁史则左氏焉得续经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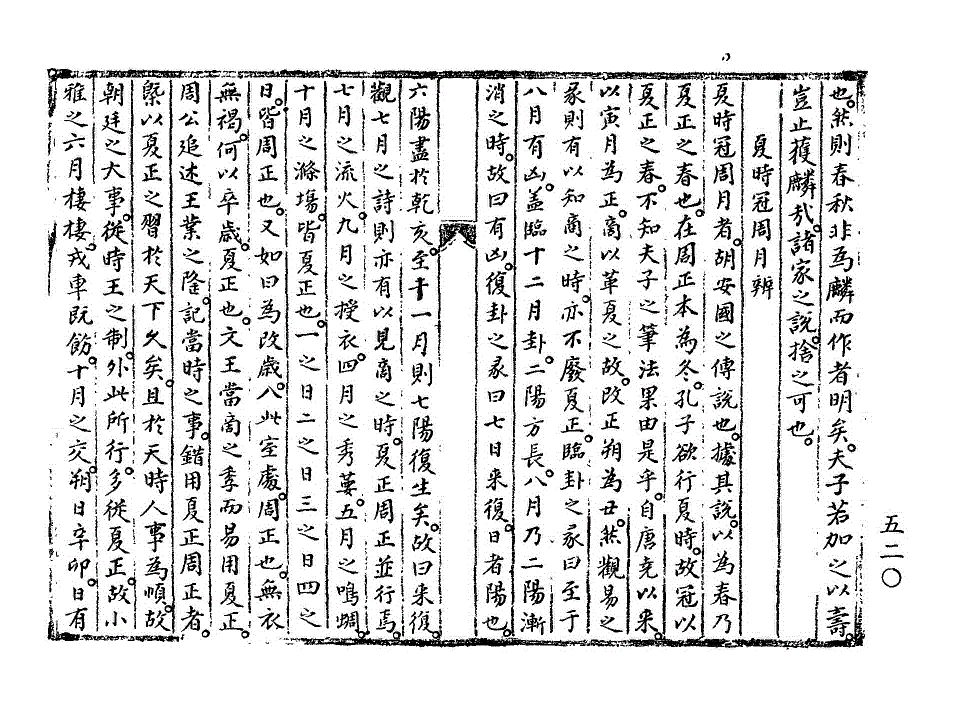 也。然则春秋非为麟而作者明矣。夫子若加之以寿。岂止获麟哉。诸家之说。舍之可也。
也。然则春秋非为麟而作者明矣。夫子若加之以寿。岂止获麟哉。诸家之说。舍之可也。夏时冠周月辨
夏时冠周月者。胡安国之传说也。据其说。以为春乃夏正之春也。在周正本为冬。孔子欲行夏时。故冠以夏正之春。不知夫子之笔法果由是乎。自唐尧以来。以寅月为正。商以革夏之故。改正朔为丑。然观易之彖则有以知商之时。亦不废夏正。临卦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盖临十二月卦。二阳方长。八月乃二阳渐消之时。故曰有凶。复卦之彖曰七日来复。日者阳也。六阳尽于乾亥。至十一月则七阳复生矣。故曰来复。观七月之诗则亦有以见商之时。夏正周正并行焉。七月之流火。九月之授衣。四月之秀葽。五月之鸣蜩。十月之涤场。皆夏正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周正也。又如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周正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夏正也。文王当商之季而易用夏正。周公追述王业之隆。记当时之事。错用夏正周正者。槩以夏正之习于天下久矣。且于天时人事为顺。故朝廷之大事。从时王之制。外此所行。多从夏正。故小雅之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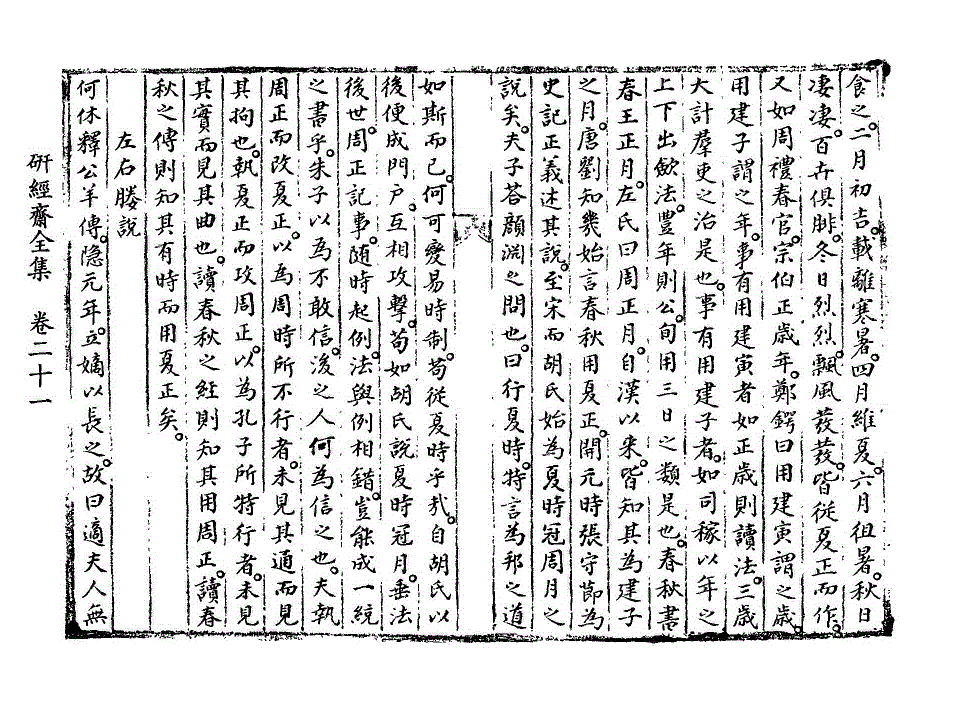 食之。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俱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皆从夏正而作。又如周礼春官。宗伯正岁年。郑锷曰用建寅谓之岁。用建子谓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岁则读法。三岁大计群吏之治是也。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礼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是也。春秋书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自汉以来。皆知其为建子之月。唐刘知几始言春秋用夏正。开元时张守节为史记正义述其说。至宋而胡氏始为夏时冠周月之说矣。夫子答颜渊之问也。曰行夏时。特言为邦之道如斯而已。何可变易时制。苟从夏时乎哉。自胡氏以后便成门户。互相攻击。苟如胡氏说夏时冠月。垂法后世。周正记事。随时起例。法与例相错。岂能成一统之书乎。朱子以为不敢信。后之人何为信之也。夫执周正而改夏正。以为周时所不行者。未见其通而见其拘也。执夏正而攻周正。以为孔子所特行者。未见其实而见其曲也。读春秋之经则知其用周正。读春秋之传则知其有时而用夏正矣。
食之。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俱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皆从夏正而作。又如周礼春官。宗伯正岁年。郑锷曰用建寅谓之岁。用建子谓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岁则读法。三岁大计群吏之治是也。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礼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是也。春秋书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自汉以来。皆知其为建子之月。唐刘知几始言春秋用夏正。开元时张守节为史记正义述其说。至宋而胡氏始为夏时冠周月之说矣。夫子答颜渊之问也。曰行夏时。特言为邦之道如斯而已。何可变易时制。苟从夏时乎哉。自胡氏以后便成门户。互相攻击。苟如胡氏说夏时冠月。垂法后世。周正记事。随时起例。法与例相错。岂能成一统之书乎。朱子以为不敢信。后之人何为信之也。夫执周正而改夏正。以为周时所不行者。未见其通而见其拘也。执夏正而攻周正。以为孔子所特行者。未见其实而见其曲也。读春秋之经则知其用周正。读春秋之传则知其有时而用夏正矣。左右媵说
何休释公羊传。隐元年。立嫡以长之。故曰适夫人无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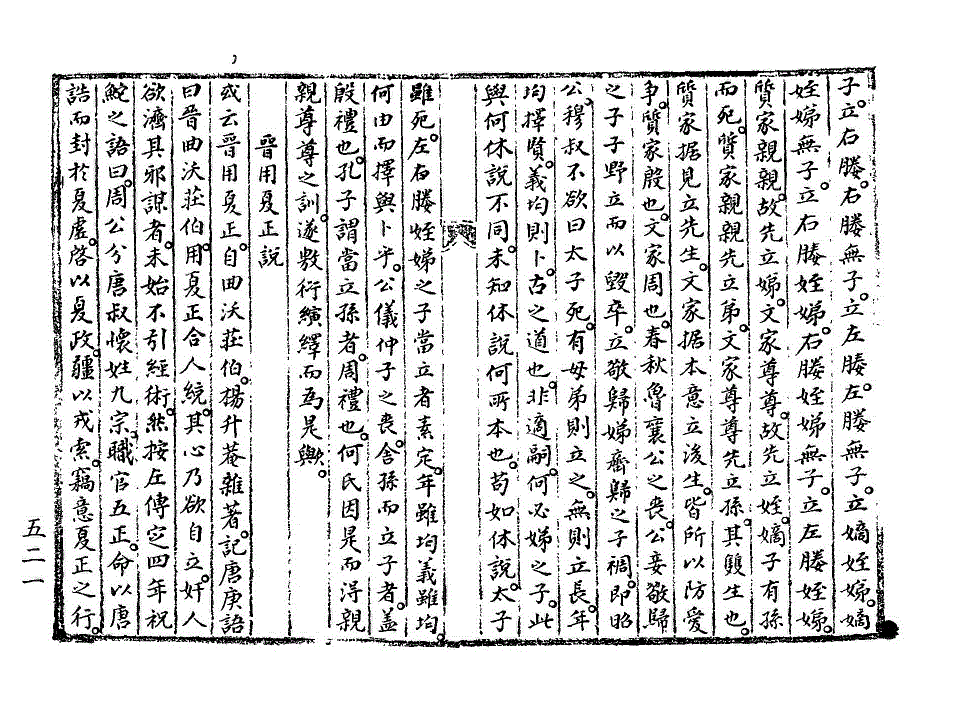 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故先立娣。文家尊尊。故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质家殷也。文家周也。春秋鲁襄公之丧。公妾敬归之子子野立而以毁卒。立敬归娣齐归之子禂。即昭公。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均择贤。义均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此与何休说不同。未知休说何所本也。苟如休说。太子虽死。左右媵侄娣之子当立者素定。年虽均义虽均。何由而择与卜乎。公仪仲子之丧。舍孙而立子者。盖殷礼也。孔子谓当立孙者。周礼也。何氏因是而得亲亲尊尊之训。遂敷衍演绎而为是欤。
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故先立娣。文家尊尊。故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质家殷也。文家周也。春秋鲁襄公之丧。公妾敬归之子子野立而以毁卒。立敬归娣齐归之子禂。即昭公。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均择贤。义均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此与何休说不同。未知休说何所本也。苟如休说。太子虽死。左右媵侄娣之子当立者素定。年虽均义虽均。何由而择与卜乎。公仪仲子之丧。舍孙而立子者。盖殷礼也。孔子谓当立孙者。周礼也。何氏因是而得亲亲尊尊之训。遂敷衍演绎而为是欤。晋用夏正说
或云晋用夏正。自曲沃庄伯。杨升庵杂著。记唐庚语曰晋曲沃庄伯。用夏正合人统。其心乃欲自立。奸人欲济其邪谋者。未始不引经术。然按左传定四年祝鮀之语曰。周公分唐叔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窃意夏正之行。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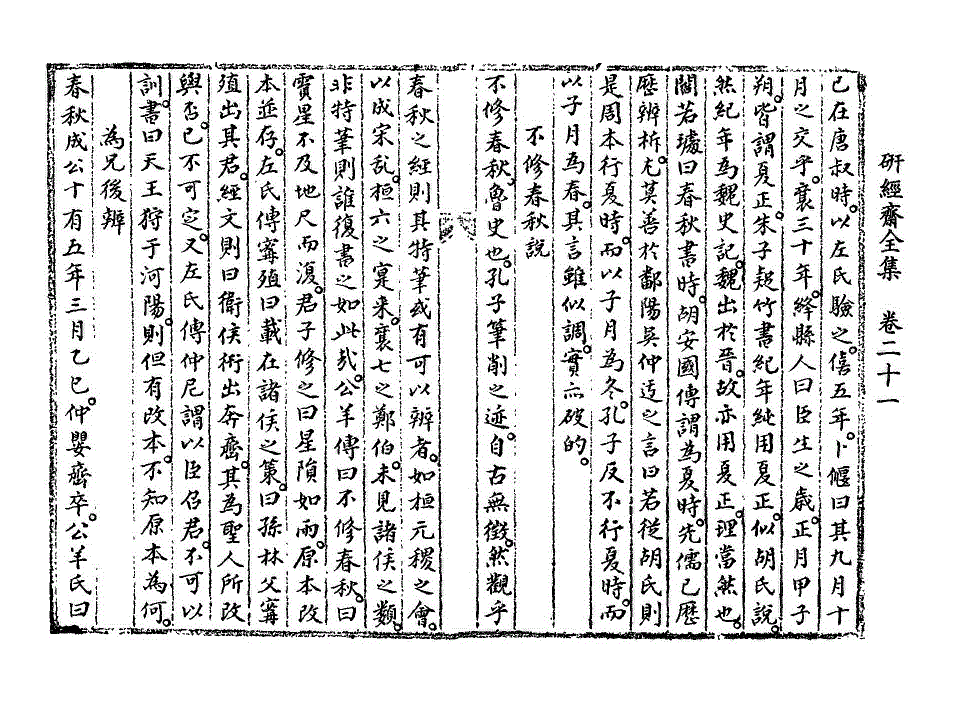 已在唐叔时。以左氏验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绛县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皆谓夏正。朱子疑竹书纪年纯用夏正。似胡氏说。然纪年为魏史记。魏出于晋。故亦用夏正。理当然也。阎若璩曰春秋书时。胡安国传谓为夏时。先儒已历历辨析。尤莫善于鄱阳吴仲迂之言曰若从胡氏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其言虽似调。实亦破的。
已在唐叔时。以左氏验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绛县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皆谓夏正。朱子疑竹书纪年纯用夏正。似胡氏说。然纪年为魏史记。魏出于晋。故亦用夏正。理当然也。阎若璩曰春秋书时。胡安国传谓为夏时。先儒已历历辨析。尤莫善于鄱阳吴仲迂之言曰若从胡氏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其言虽似调。实亦破的。不修春秋说
不修春秋。鲁史也。孔子笔削之迹。自古无徵。然观乎春秋之经则其特笔或有可以辨者。如桓元稷之会。以成宋乱。桓六之寔来。襄七之郑伯。未见诸侯之类。非特笔则谁复书之如此哉。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原本改本并存。左氏传宁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又左氏传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
为兄后辨
春秋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公羊氏曰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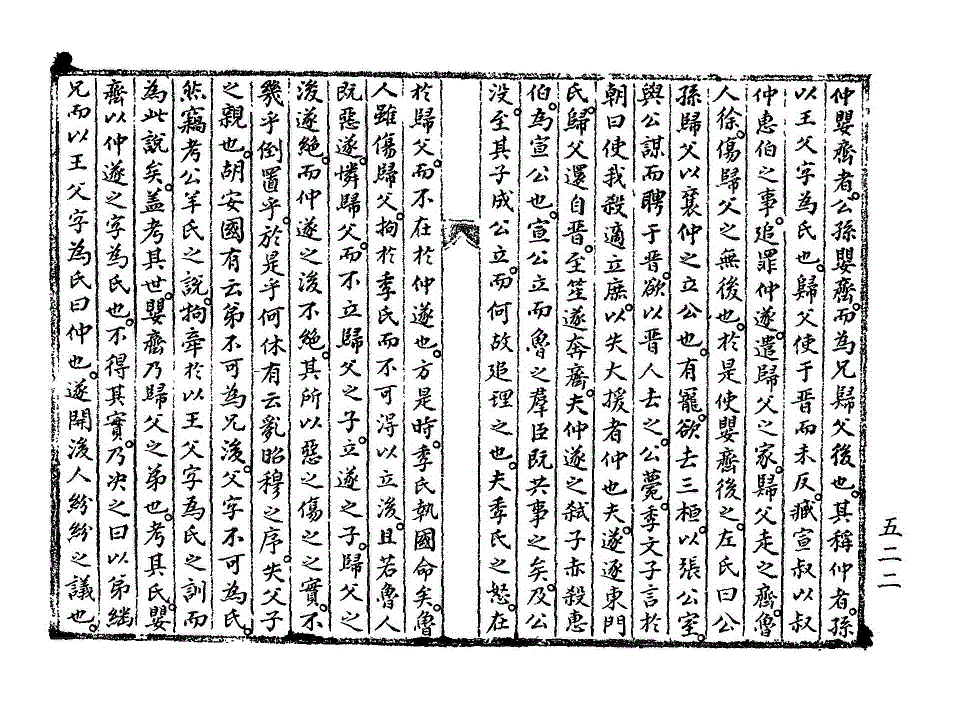 仲婴齐者。公孙婴齐。而为兄归父后也。其称仲者。孙以王父字为氏也。归父使于晋而未反。臧宣叔以叔仲惠伯之事。追罪仲遂。遣归父之家。归父走之齐。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左氏曰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东门氏。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夫仲遂之弑子赤杀惠伯。为宣公也。宣公立而鲁之群臣既共事之矣。及公没。至其子成公立。而何故追理之也。夫季氏之怒。在于归父。而不在于仲遂也。方是时。季氏执国命矣。鲁人虽伤归父。拘于季氏而不可得以立后。且若鲁人既恶遂。怜归父。而不立归父之子。立遂之子。归父之后遂绝。而仲遂之后不绝。其所以恶之伤之之实。不几乎倒置乎。于是乎何休有云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也。胡安国有云弟不可为兄后。父字不可为氏。然窃考公羊氏之说。拘牵于以王父字为氏之训而为此说矣。盖考其世。婴齐乃归父之弟也。考其氏。婴齐以仲遂之字为氏也。不得其实。乃决之曰以弟继兄而以王父字为氏曰仲也。遂开后人纷纷之议也。
仲婴齐者。公孙婴齐。而为兄归父后也。其称仲者。孙以王父字为氏也。归父使于晋而未反。臧宣叔以叔仲惠伯之事。追罪仲遂。遣归父之家。归父走之齐。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左氏曰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东门氏。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夫仲遂之弑子赤杀惠伯。为宣公也。宣公立而鲁之群臣既共事之矣。及公没。至其子成公立。而何故追理之也。夫季氏之怒。在于归父。而不在于仲遂也。方是时。季氏执国命矣。鲁人虽伤归父。拘于季氏而不可得以立后。且若鲁人既恶遂。怜归父。而不立归父之子。立遂之子。归父之后遂绝。而仲遂之后不绝。其所以恶之伤之之实。不几乎倒置乎。于是乎何休有云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也。胡安国有云弟不可为兄后。父字不可为氏。然窃考公羊氏之说。拘牵于以王父字为氏之训而为此说矣。盖考其世。婴齐乃归父之弟也。考其氏。婴齐以仲遂之字为氏也。不得其实。乃决之曰以弟继兄而以王父字为氏曰仲也。遂开后人纷纷之议也。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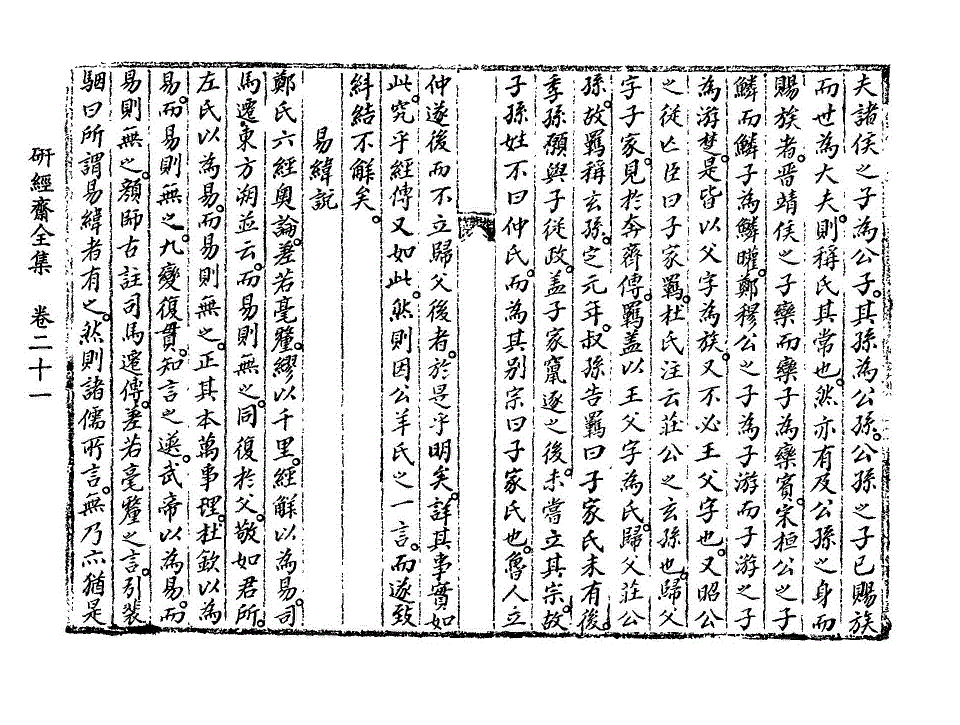 夫诸侯之子为公子。其孙为公孙。公孙之子已赐族而世为大夫。则称氏其常也。然亦有及公孙之身而赐族者。晋靖侯之子栾而栾子为栾宾。宋桓公之子鳞而鳞子为鳞𣌓。郑穆公之子为子游而子游之子为游楚。是皆以父字为族。又不必王父字也。又昭公之从亡臣曰子家羁。杜氏注云庄公之玄孙也。归父字子家。见于奔齐传。羁盖以王父字为氏。归父庄公孙。故羁称玄孙。定元年。叔孙告羁曰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盖子家窜逐之后。未尝立其宗。故子孙姓不曰仲氏。而为其别宗曰子家氏也。鲁人立仲遂后而不立归父后者。于是乎明矣。详其事实如此。究乎经传又如此。然则因公羊氏之一言。而遂致纠结不解矣。
夫诸侯之子为公子。其孙为公孙。公孙之子已赐族而世为大夫。则称氏其常也。然亦有及公孙之身而赐族者。晋靖侯之子栾而栾子为栾宾。宋桓公之子鳞而鳞子为鳞𣌓。郑穆公之子为子游而子游之子为游楚。是皆以父字为族。又不必王父字也。又昭公之从亡臣曰子家羁。杜氏注云庄公之玄孙也。归父字子家。见于奔齐传。羁盖以王父字为氏。归父庄公孙。故羁称玄孙。定元年。叔孙告羁曰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盖子家窜逐之后。未尝立其宗。故子孙姓不曰仲氏。而为其别宗曰子家氏也。鲁人立仲遂后而不立归父后者。于是乎明矣。详其事实如此。究乎经传又如此。然则因公羊氏之一言。而遂致纠结不解矣。易纬说
郑氏六经奥论。差若毫釐。缪以千里。经解以为易。司马迁,东方朔并云。而易则无之。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左氏以为易。而易则无之。正其本万事理。杜钦以为易。而易则无之。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武帝以为易。而易则无之。颜师古注司马迁传。差若毫釐之言。引裴骃曰所谓易纬者有之。然则诸儒所言。无乃亦犹是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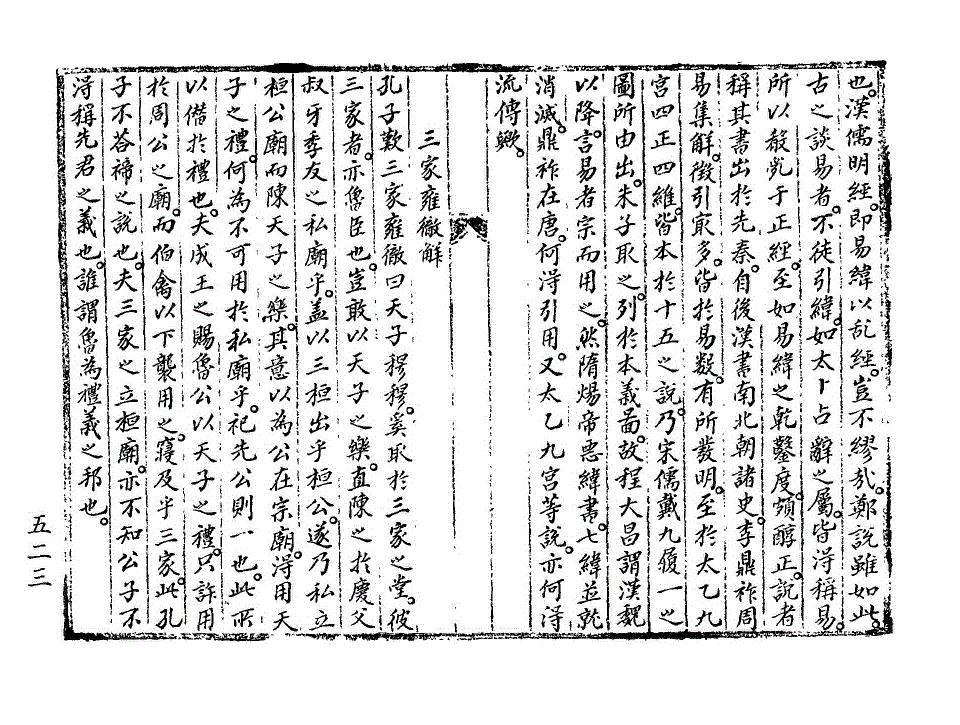 也。汉儒明经。即易纬以乱经。岂不缪哉。郑说虽如此。古之谈易者。不徒引纬。如太卜占辞之属。皆得称易。所以殽乱于正经。至如易纬之乾凿度。颇醇正。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李鼎祚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于易数。有所发明。至于太乙九宫四正四维。皆本于十五之说。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图所由出。朱子取之。列于本义啚。故程大昌谓汉魏以降。言易者宗而用之。然隋炀帝恶纬书。七纬并就消灭。鼎祚在唐。何得引用。又太乙九宫等说。亦何得流传欤。
也。汉儒明经。即易纬以乱经。岂不缪哉。郑说虽如此。古之谈易者。不徒引纬。如太卜占辞之属。皆得称易。所以殽乱于正经。至如易纬之乾凿度。颇醇正。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李鼎祚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于易数。有所发明。至于太乙九宫四正四维。皆本于十五之说。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图所由出。朱子取之。列于本义啚。故程大昌谓汉魏以降。言易者宗而用之。然隋炀帝恶纬书。七纬并就消灭。鼎祚在唐。何得引用。又太乙九宫等说。亦何得流传欤。三家雍彻解
孔子叹三家雍彻曰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彼三家者。亦鲁臣也。岂敢以天子之乐。直陈之于庆父叔牙季友之私庙乎。盖以三桓出乎桓公。遂乃私立桓公庙而陈天子之乐。其意以为公在宗庙。得用天子之礼。何为不可用于私庙乎。祀先公则一也。此所以僭于礼也。夫成王之赐鲁公以天子之礼。只许用于周公之庙。而伯禽以下袭用之。寝及乎三家。此孔子不答禘之说也。夫三家之立桓庙。亦不知公子不得称先君之义也。谁谓鲁为礼义之邦也。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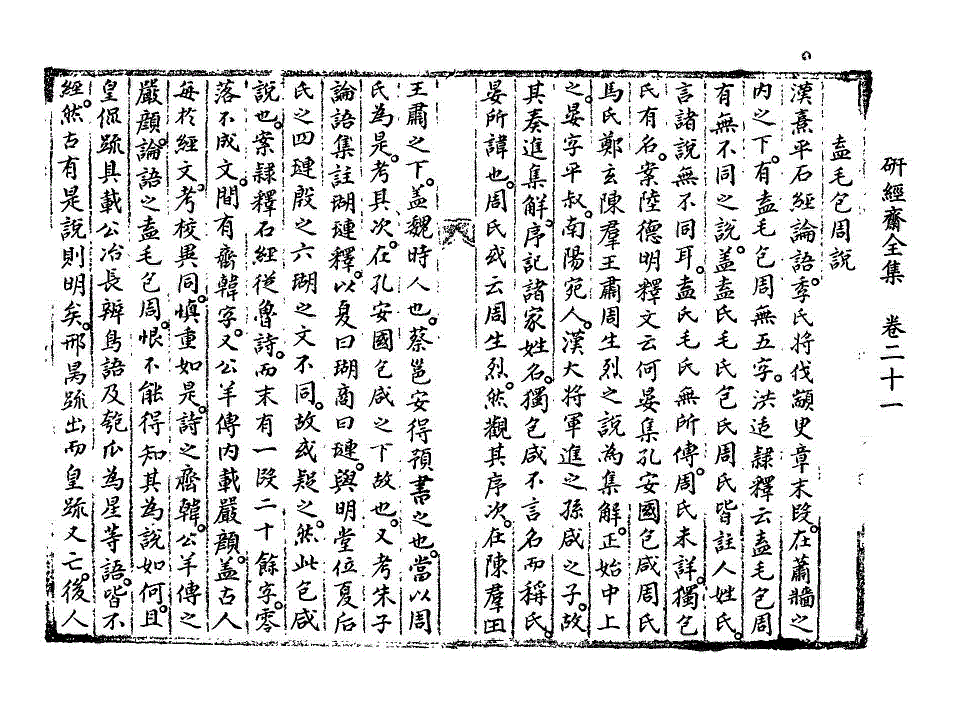 盍毛包周说
盍毛包周说汉熹平石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章末段。在萧墙之内之下。有盍毛包周无五字。洪适隶释云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盖盍氏毛氏包氏周氏皆注人姓氏。言诸说无不同耳。盍氏毛氏无所传。周氏未详。独包氏有名。案陆德明释文云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为集解。正始中上之。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汉大将军进之孙咸之子。故其奏进集解。序记诸家姓名。独包咸不言名而称氏。晏所讳也。周氏或云周生烈。然观其序次。在陈群田王肃之下。盖魏时人也。蔡邕安得预书之也。当以周氏为是。考其次。在孔安国包咸之下故也。又考朱子论语集注瑚琏释。以夏曰瑚商曰琏。与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之文不同。故或疑之。然此包咸说也。案隶释石经从鲁诗。而末有一段二十馀字。零落不成文。间有齐韩字。又公羊传内载严颜。盖古人每于经文。考校异同。慎重如是。诗之齐韩。公羊传之严颜。论语之盍毛包周。恨不能得知其为说如何。且皇侃疏具载公冶长辨鸟语及匏瓜为星等语。皆不经。然古有是说则明矣。邢炳疏出而皇疏又亡。后人
研经斋全集卷之二十一 第 5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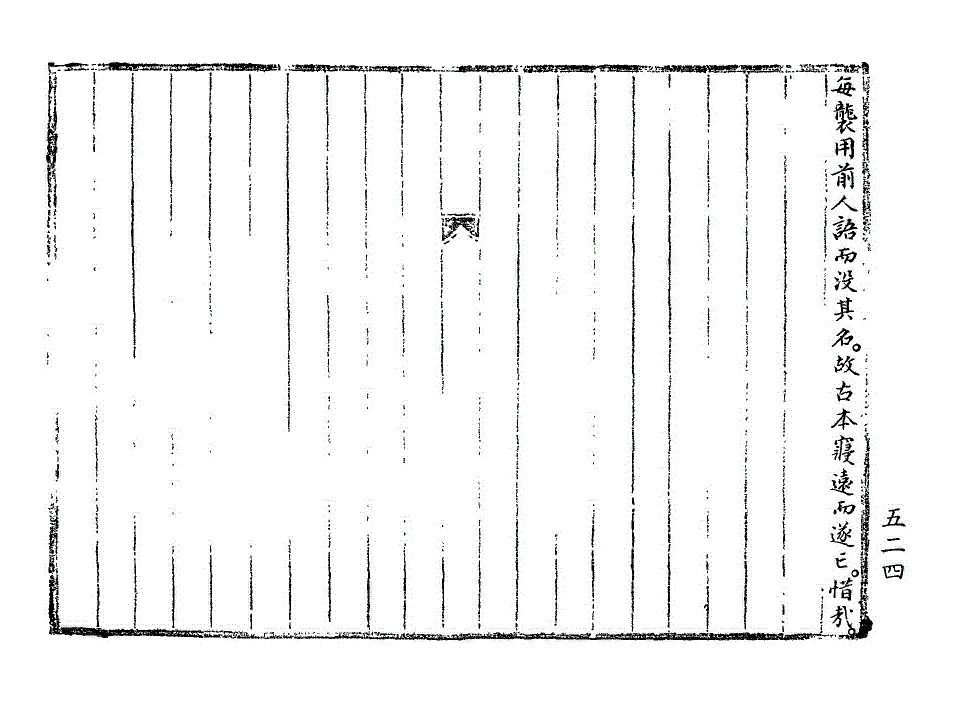 每袭用前人语而没其名。故古本寝远而遂亡。惜哉。
每袭用前人语而没其名。故古本寝远而遂亡。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