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x 页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经解
经解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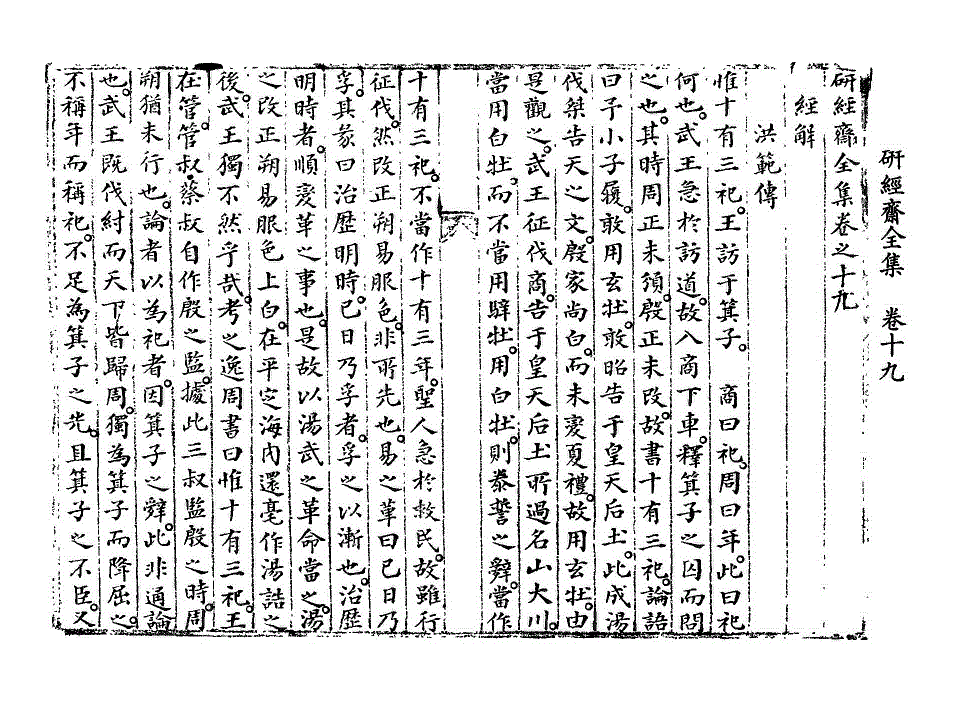 洪范传
洪范传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何也。武王急于访道。故入商下车。释箕子之囚而问之也。其时周正未颁。殷正未改。故书十有三祀。论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此成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而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由是观之。武王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当用白牡。而不当用骍牡。用白牡。则泰誓之辞。当作十有三祀。不当作十有三年。圣人急于救民。故虽行征伐。然改正朔易服色。非所先也。易之革曰已日乃孚。其彖曰治历明时。已日乃孚者。孚之以渐也。治历明时者。顺变革之事也。是故以汤武之革命当之。汤之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在平定海内还亳作汤诰之后。武王独不然乎哉。考之逸周书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监。据此三叔监殷之时。周朔犹未行也。论者以为祀者。因箕子之辞。此非通论也。武王既伐纣而天下皆归周。独为箕子而降屈之。不称年而称祀。不足为箕子之先。且箕子之不臣。又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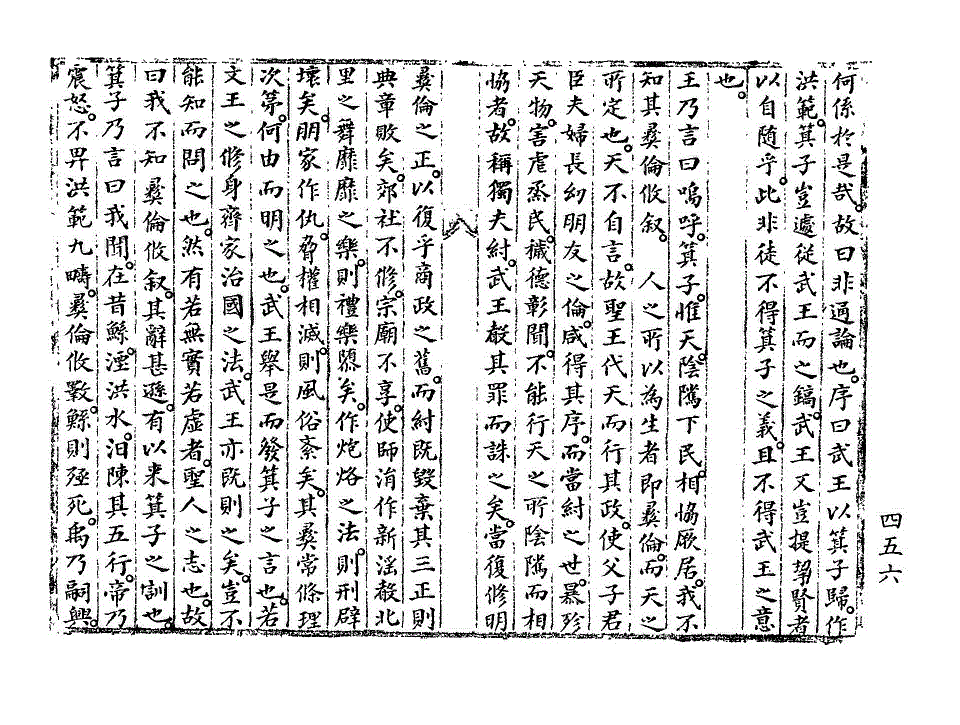 何系于是哉。故曰非通论也。序曰武王以箕子归。作洪范。箕子岂遽从武王而之镐。武王又岂提挈贤者以自随乎。此非徒不得箕子之义。且不得武王之意也。
何系于是哉。故曰非通论也。序曰武王以箕子归。作洪范。箕子岂遽从武王而之镐。武王又岂提挈贤者以自随乎。此非徒不得箕子之义。且不得武王之意也。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人之所以为生者即彝伦。而天之所定也。天不自言。故圣王代天而行其政。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咸得其序。而当纣之世。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秽德彰闻。不能行天之所阴骘而相协者。故称独夫纣。武王声其罪而诛之矣。当复修明彝伦之正。以复乎商政之旧。而纣既毁弃其三正则典章败矣。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则礼乐隳矣。作炮烙之法。则刑辟坏矣。朋家作仇。胁权相灭。则风俗紊矣。其彝常条理次第。何由而明之也。武王举是而发箕子之言也。若文王之修身齐家治国之法。武王亦既则之矣。岂不能知而问之也。然有若无实若虚者。圣人之志也。故曰我不知彝伦攸叙。其辞甚逊。有以来箕子之训也。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7H 页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武王之问。即伦常之事。而箕子之对。远引鲧禹之事何也。不忍言殷恶也。帝者为谁。曰尧也。尧之时。怀襄之灾极矣。鲧悻直自用。乃欲障而塞之。水不益冲决坏乱乎。尧知其方命圮族而命之者。以其才干可足用也。夫顺则行逆则违。天下之通理也。鲧失之而水益汎滥于中国。蛇龙益纵横。而常伦于是乎斁矣。禹得之而江淮河汉。各循其流。鸟兽之害皆去。而常伦于是乎叙矣。有以见才之不可恃。而理之不可拂也。洪范九畴者何也。洪范。帝王之大法。九畴者。其目也。自尧舜禹以来。皆以精一执中之心法相传。然其治道政术。未有以详细条理。以为一统之典。则禹始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嗣是而又以世相传。楚辞所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而自纵者是也。其法传至箕子而始克大脩。如周文王得伏羲之卦而为之彖也。是故明夷之传。以箕子文王并称之。夫帝王之大法。彝伦之所以行也。帝之所以不畀者。天之所以锡者。于何乎考之哉。从其诛殛谴罚之迹而言之则知帝之所以威而靳之也。从其敷土随山之迹而观之则知天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武王之问。即伦常之事。而箕子之对。远引鲧禹之事何也。不忍言殷恶也。帝者为谁。曰尧也。尧之时。怀襄之灾极矣。鲧悻直自用。乃欲障而塞之。水不益冲决坏乱乎。尧知其方命圮族而命之者。以其才干可足用也。夫顺则行逆则违。天下之通理也。鲧失之而水益汎滥于中国。蛇龙益纵横。而常伦于是乎斁矣。禹得之而江淮河汉。各循其流。鸟兽之害皆去。而常伦于是乎叙矣。有以见才之不可恃。而理之不可拂也。洪范九畴者何也。洪范。帝王之大法。九畴者。其目也。自尧舜禹以来。皆以精一执中之心法相传。然其治道政术。未有以详细条理。以为一统之典。则禹始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嗣是而又以世相传。楚辞所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而自纵者是也。其法传至箕子而始克大脩。如周文王得伏羲之卦而为之彖也。是故明夷之传。以箕子文王并称之。夫帝王之大法。彝伦之所以行也。帝之所以不畀者。天之所以锡者。于何乎考之哉。从其诛殛谴罚之迹而言之则知帝之所以威而靳之也。从其敷土随山之迹而观之则知天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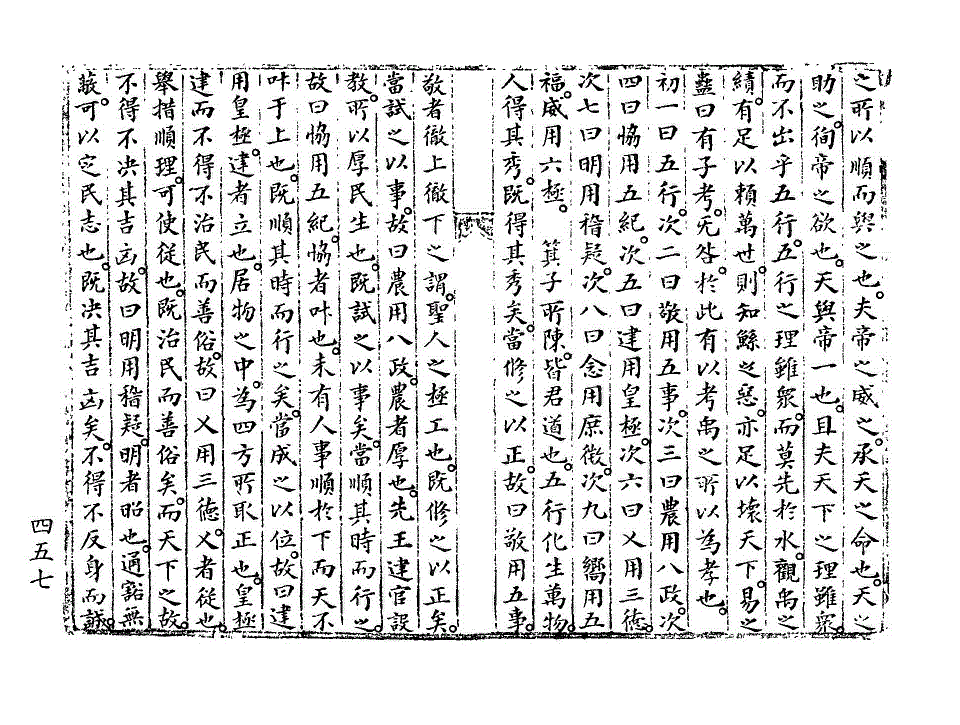 之所以顺而与之也。夫帝之威之。承天之命也。天之助之。徇帝之欲也。天与帝一也。且夫天下之理虽众。而不出乎五行。五行之理虽众。而莫先于水。观禹之绩。有足以赖万世。则知鲧之恶。亦足以坏天下。易之蛊曰有子考。无咎。于此有以考禹之所以为孝也。
之所以顺而与之也。夫帝之威之。承天之命也。天之助之。徇帝之欲也。天与帝一也。且夫天下之理虽众。而不出乎五行。五行之理虽众。而莫先于水。观禹之绩。有足以赖万世。则知鲧之恶。亦足以坏天下。易之蛊曰有子考。无咎。于此有以考禹之所以为孝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箕子所陈。皆君道也。五行化生万物。人得其秀。既得其秀矣。当修之以正。故曰敬用五事。敬者彻上彻下之谓。圣人之极工也。既修之以正矣。当试之以事。故曰农用八政。农者厚也。先王建官设教。所以厚民生也。既试之以事矣。当顺其时而行之。故曰协用五纪。协者叶也。未有人事顺于下而天不叶于上也。既顺其时而行之矣。当成之以位。故曰建用皇极。建者立也。居物之中。为四方所取正也。皇极建而不得不治民而善俗。故曰乂用三德。乂者从也。举措顺理。可使从也。既治民而善俗矣。而天下之故。不得不决其吉凶。故曰明用稽疑。明者昭也。通豁无蔽。可以定民志也。既决其吉凶矣。不得不反身而诚。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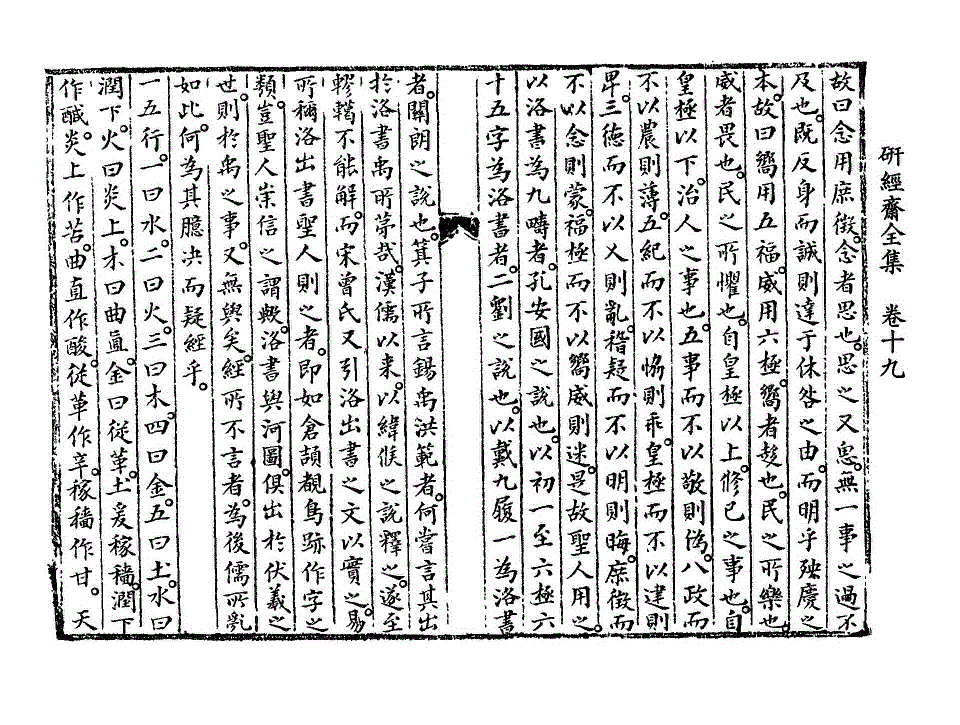 故曰念用庶徵。念者思也。思之又思。无一事之过不及也。既反身而诚则达于休咎之由。而明乎殃庆之本。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向者趍也。民之所乐也。威者畏也。民之所惧也。自皇极以上。修己之事也。自皇极以下。治人之事也。五事而不以敬则伪。八政而不以农则薄。五纪而不以协则乖。皇极而不以建则卑。三德而不以乂则乱。稽疑而不以明则晦。庶徵而不以念则蒙。福极而不以向威则迷。是故圣人用之。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也。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也。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也。箕子所言锡禹洪范者。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哉。汉儒以来。以纬候之说释之。遂至轇轕不能解。而宋曾氏又引洛出书之文以实之。易所称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即如仓颉睹鸟迹作字之类。岂圣人崇信之谓欤。洛书与河图。俱出于伏羲之世。则于禹之事。又无与矣。经所不言者。为后儒所乱如此。何为其臆决而疑经乎。
故曰念用庶徵。念者思也。思之又思。无一事之过不及也。既反身而诚则达于休咎之由。而明乎殃庆之本。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向者趍也。民之所乐也。威者畏也。民之所惧也。自皇极以上。修己之事也。自皇极以下。治人之事也。五事而不以敬则伪。八政而不以农则薄。五纪而不以协则乖。皇极而不以建则卑。三德而不以乂则乱。稽疑而不以明则晦。庶徵而不以念则蒙。福极而不以向威则迷。是故圣人用之。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也。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也。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也。箕子所言锡禹洪范者。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哉。汉儒以来。以纬候之说释之。遂至轇轕不能解。而宋曾氏又引洛出书之文以实之。易所称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即如仓颉睹鸟迹作字之类。岂圣人崇信之谓欤。洛书与河图。俱出于伏羲之世。则于禹之事。又无与矣。经所不言者。为后儒所乱如此。何为其臆决而疑经乎。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天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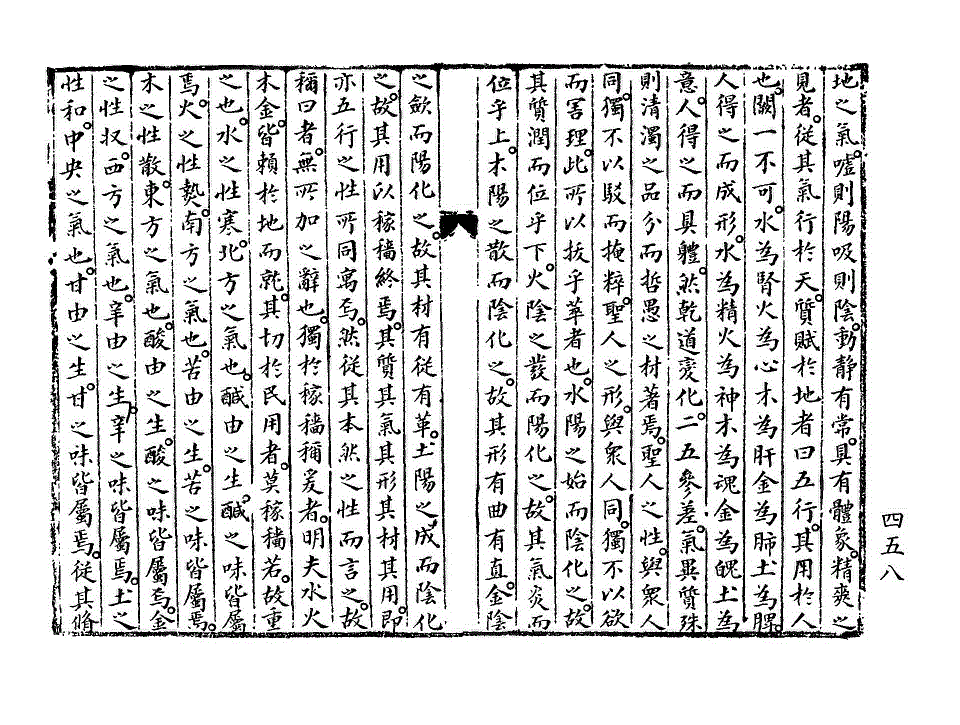 地之气。嘘则阳吸则阴。动静有常。具有体象。精爽之见者。从其气行于天。质赋于地者曰五行。其用于人也。阙一不可。水为肾火为心木为肝金为肺土为脾。人得之而成形。水为精火为神木为魂金为魄土为意。人得之而具体。然乾道变化。二五参差。气异质殊则清浊之品分而哲愚之材著焉。圣人之性。与众人同。独不以驳而掩粹。圣人之形。与众人同。独不以欲而害理。此所以拔乎萃者也。水阳之始而阴化之。故其质润而位乎下。火阴之发而阳化之。故其气炎而位乎上。木阳之散而阴化之。故其形有曲有直。金阴之敛而阳化之。故其材有从有革。土阳之成而阴化之。故其用以稼穑终焉。其质其气其形其材其用。即亦五行之性所同寓焉。然从其本然之性而言之。故称曰者。无所加之辞也。独于稼穑称爰者。明夫水火木金。皆赖于地而就。其切于民用者。莫稼穑若。故重之也。水之性寒。北方之气也。咸由之生。咸之味皆属焉。火之性热。南方之气也。苦由之生。苦之味皆属焉。木之性散。东方之气也。酸由之生。酸之味皆属焉。金之性收。西方之气也。辛由之生。辛之味皆属焉。土之性和。中央之气也。甘由之生。甘之味皆属焉。从其脩
地之气。嘘则阳吸则阴。动静有常。具有体象。精爽之见者。从其气行于天。质赋于地者曰五行。其用于人也。阙一不可。水为肾火为心木为肝金为肺土为脾。人得之而成形。水为精火为神木为魂金为魄土为意。人得之而具体。然乾道变化。二五参差。气异质殊则清浊之品分而哲愚之材著焉。圣人之性。与众人同。独不以驳而掩粹。圣人之形。与众人同。独不以欲而害理。此所以拔乎萃者也。水阳之始而阴化之。故其质润而位乎下。火阴之发而阳化之。故其气炎而位乎上。木阳之散而阴化之。故其形有曲有直。金阴之敛而阳化之。故其材有从有革。土阳之成而阴化之。故其用以稼穑终焉。其质其气其形其材其用。即亦五行之性所同寓焉。然从其本然之性而言之。故称曰者。无所加之辞也。独于稼穑称爰者。明夫水火木金。皆赖于地而就。其切于民用者。莫稼穑若。故重之也。水之性寒。北方之气也。咸由之生。咸之味皆属焉。火之性热。南方之气也。苦由之生。苦之味皆属焉。木之性散。东方之气也。酸由之生。酸之味皆属焉。金之性收。西方之气也。辛由之生。辛之味皆属焉。土之性和。中央之气也。甘由之生。甘之味皆属焉。从其脩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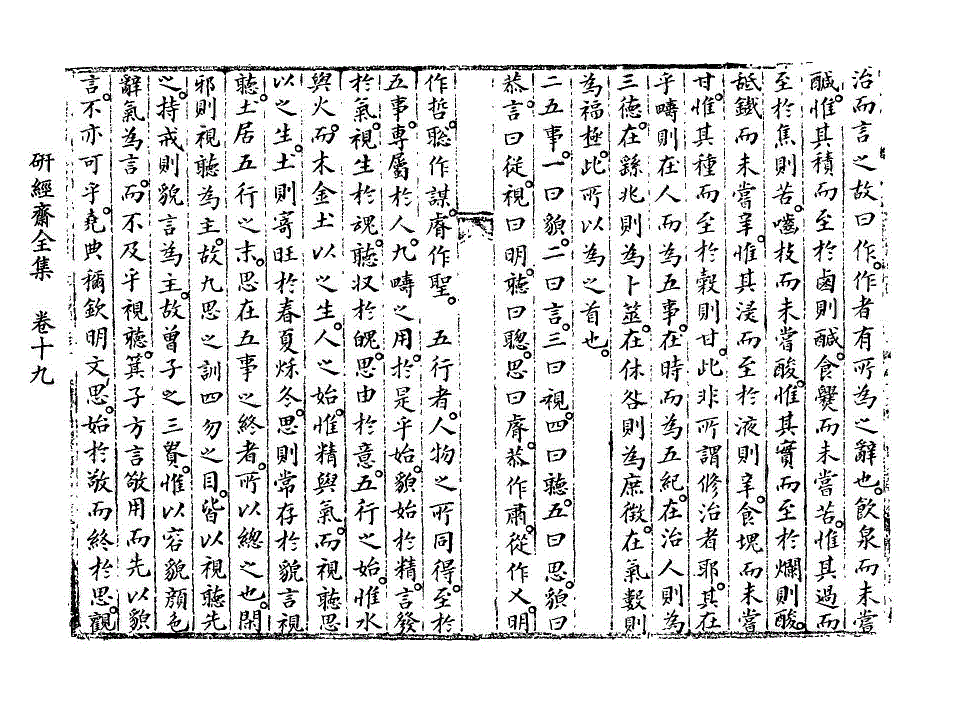 治而言之故曰作。作者有所为之辞也。饮泉而未尝咸。惟其积而至于卤则咸。食爨而未尝苦。惟其过而至于焦则苦。啮枝而未尝酸。惟其实而至于烂则酸。舐铁而未尝辛。惟其浸而至于液则辛。食块而未尝甘。惟其种而至于谷则甘。此非所谓修治者耶。其在乎畴则在人而为五事。在时而为五纪。在治人则为三德。在繇兆则为卜筮。在休咎则为庶徵。在气数则为福极。此所以为之首也。
治而言之故曰作。作者有所为之辞也。饮泉而未尝咸。惟其积而至于卤则咸。食爨而未尝苦。惟其过而至于焦则苦。啮枝而未尝酸。惟其实而至于烂则酸。舐铁而未尝辛。惟其浸而至于液则辛。食块而未尝甘。惟其种而至于谷则甘。此非所谓修治者耶。其在乎畴则在人而为五事。在时而为五纪。在治人则为三德。在繇兆则为卜筮。在休咎则为庶徵。在气数则为福极。此所以为之首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五行者。人物之所同得。至于五事。专属于人。九畴之用。于是乎始。貌始于精。言发于气。视生于魂。听收于魄。思由于意。五行之始。惟水与火。而木金土以之生。人之始。惟精与气。而视听思以之生。土则寄旺于春夏秋冬。思则常存于貌言视听。土居五行之末。思在五事之终者。所以总之也。闲邪则视听为主。故九思之训四勿之目。皆以视听先之。持戒则貌言为主。故曾子之三贵。惟以容貌颜色辞气为言。而不及乎视听。箕子方言敬用而先以貌言。不亦可乎。尧典称钦明文思。始于敬而终于思。观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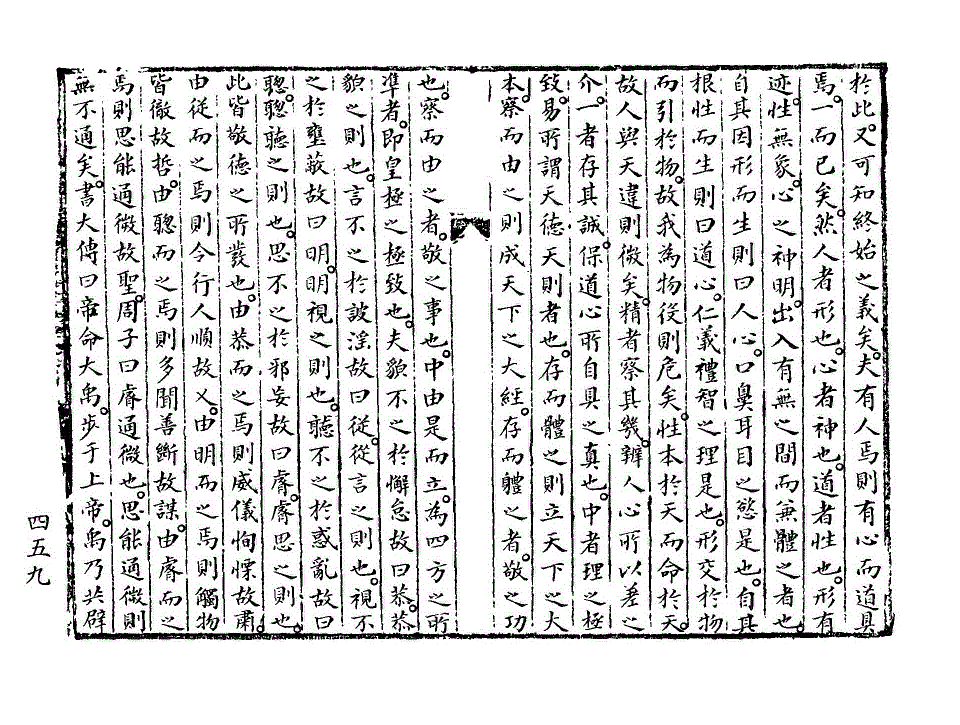 于此。又可知终始之义矣。夫有人焉则有心而道具焉。一而已矣。然人者形也。心者神也。道者性也。形有迹。性无象。心之神明。出入有无之间而兼体之者也。自其因形而生则曰人心。口鼻耳目之欲是也。自其根性而生则曰道心。仁义礼智之理是也。形交于物而引于物。故我为物役则危矣。性本于天而命于天。故人与天违则微矣。精者察其几。辨人心所以差之介。一者存其诚。保道心所自具之真也。中者理之极致。易所谓天德天则者也。存而体之则立天下之大本。察而由之则成天下之大经。存而体之者。敬之功也。察而由之者。敬之事也。中由是而立。为四方之所准者。即皇极之极致也。夫貌不之于懈怠故曰恭。恭貌之则也。言不之于诐淫故曰从。从言之则也。视不之于壅蔽故曰明。明视之则也。听不之于惑乱故曰聪。聪听之则也。思不之于邪妄故曰睿。睿思之则也。此皆敬德之所发也。由恭而之焉则威仪恂慄故肃。由从而之焉则令行人顺故乂。由明而之焉则触物皆彻故哲。由聪而之焉则多闻善断故谋。由睿而之焉则思能通微故圣。周子曰睿通微也。思能通微则无不通矣。书大传曰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
于此。又可知终始之义矣。夫有人焉则有心而道具焉。一而已矣。然人者形也。心者神也。道者性也。形有迹。性无象。心之神明。出入有无之间而兼体之者也。自其因形而生则曰人心。口鼻耳目之欲是也。自其根性而生则曰道心。仁义礼智之理是也。形交于物而引于物。故我为物役则危矣。性本于天而命于天。故人与天违则微矣。精者察其几。辨人心所以差之介。一者存其诚。保道心所自具之真也。中者理之极致。易所谓天德天则者也。存而体之则立天下之大本。察而由之则成天下之大经。存而体之者。敬之功也。察而由之者。敬之事也。中由是而立。为四方之所准者。即皇极之极致也。夫貌不之于懈怠故曰恭。恭貌之则也。言不之于诐淫故曰从。从言之则也。视不之于壅蔽故曰明。明视之则也。听不之于惑乱故曰聪。聪听之则也。思不之于邪妄故曰睿。睿思之则也。此皆敬德之所发也。由恭而之焉则威仪恂慄故肃。由从而之焉则令行人顺故乂。由明而之焉则触物皆彻故哲。由聪而之焉则多闻善断故谋。由睿而之焉则思能通微故圣。周子曰睿通微也。思能通微则无不通矣。书大传曰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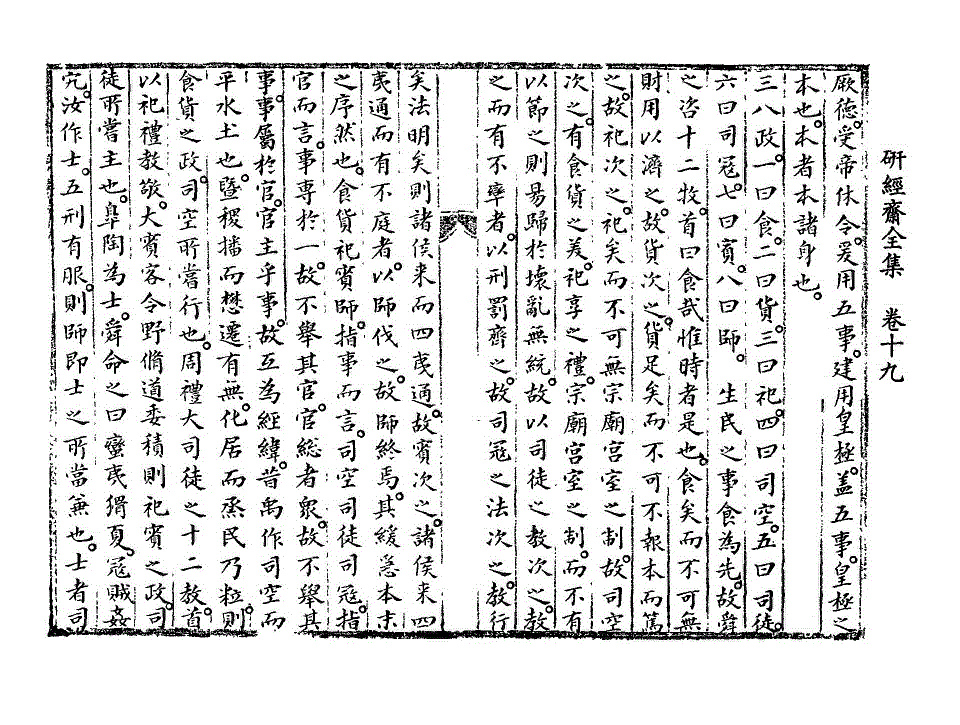 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皇极。盖五事。皇极之本也。本者本诸身也。
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皇极。盖五事。皇极之本也。本者本诸身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生民之事食为先。故舜之咨十二牧。首曰食哉惟时者是也。食矣而不可无财用以济之。故货次之。货足矣而不可不报本而笃之。故祀次之。祀矣而不可无宗庙宫室之制。故司空次之。有食货之美。祀享之礼。宗庙宫室之制。而不有以节之则易归于坏乱无统。故以司徒之教次之。教之而有不率者。以刑罚齐之。故司寇之法次之。教行矣法明矣则诸侯来而四夷通。故宾次之。诸侯来四夷通而有不庭者。以师伐之。故师终焉。其缓急本末之序然也。食货祀宾师。指事而言。司空司徒司寇。指官而言。事专于一。故不举其官。官总者众。故不举其事。事属于官。官主乎事。故互为经纬。昔禹作司空而平水土也。暨稷播而懋迁有无。化居而烝民乃粒。则食货之政。司空所尝行也。周礼大司徒之十二教。首以祀礼教敬。大宾客令野脩道委积则祀宾之政。司徒所尝主也。皋陶为士。舜命之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则师即士之所当兼也。士者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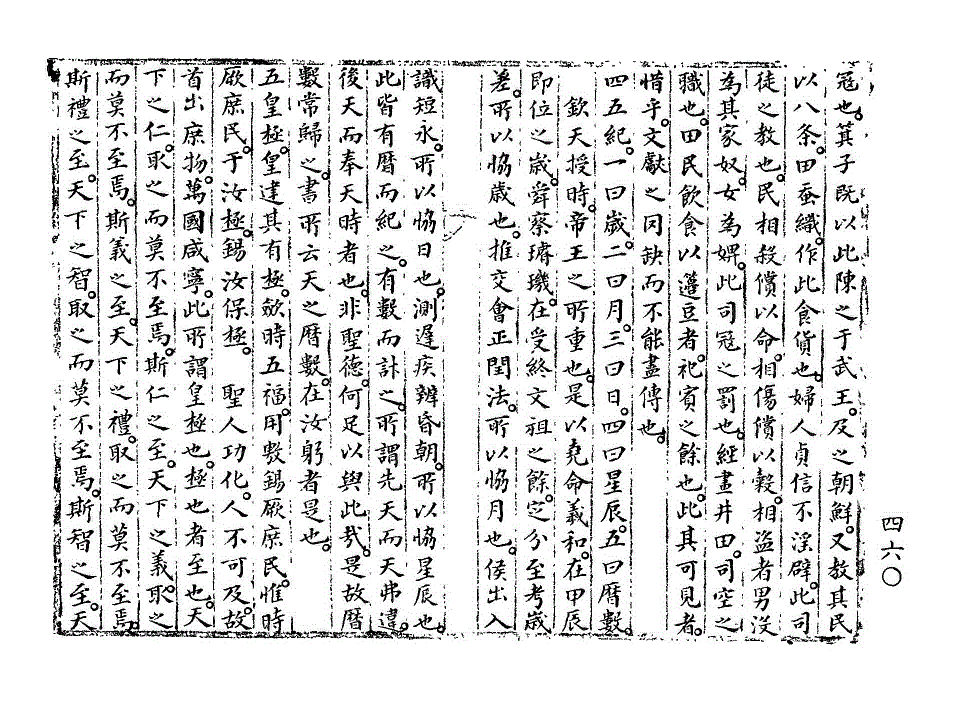 寇也。箕子既以此陈之于武王。及之朝鲜。又教其民以八条。田蚕织。作此食货也。妇人贞信不淫辟。此司徒之教也。民相杀偿以命。相伤偿以谷。相盗者男没为其家奴。女为婢。此司寇之罚也。经画井田。司空之职也。田民饮食以笾豆者。祀宾之馀也。此其可见者。惜乎。文献之罔缺而不能尽传也。
寇也。箕子既以此陈之于武王。及之朝鲜。又教其民以八条。田蚕织。作此食货也。妇人贞信不淫辟。此司徒之教也。民相杀偿以命。相伤偿以谷。相盗者男没为其家奴。女为婢。此司寇之罚也。经画井田。司空之职也。田民饮食以笾豆者。祀宾之馀也。此其可见者。惜乎。文献之罔缺而不能尽传也。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钦天授时。帝王之所重也。是以尧命羲和。在甲辰即位之岁。舜察璿玑。在受终文祖之馀。定分至考岁差。所以协岁也。推交会正闰法。所以协月也。侯出入识短永。所以协日也。测迟疾辨昏朝。所以协星辰也。此皆有历而纪之。有数而计之。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也。非圣德。何足以与此哉。是故历数常归之。书所云天之历数。在汝躬者是也。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圣人功化。人不可及。故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所谓皇极也。极也者至也。天下之仁。取之而莫不至焉。斯仁之至。天下之义。取之而莫不至焉。斯义之至。天下之礼。取之而莫不至焉。斯礼之至。天下之智。取之而莫不至焉。斯智之至。天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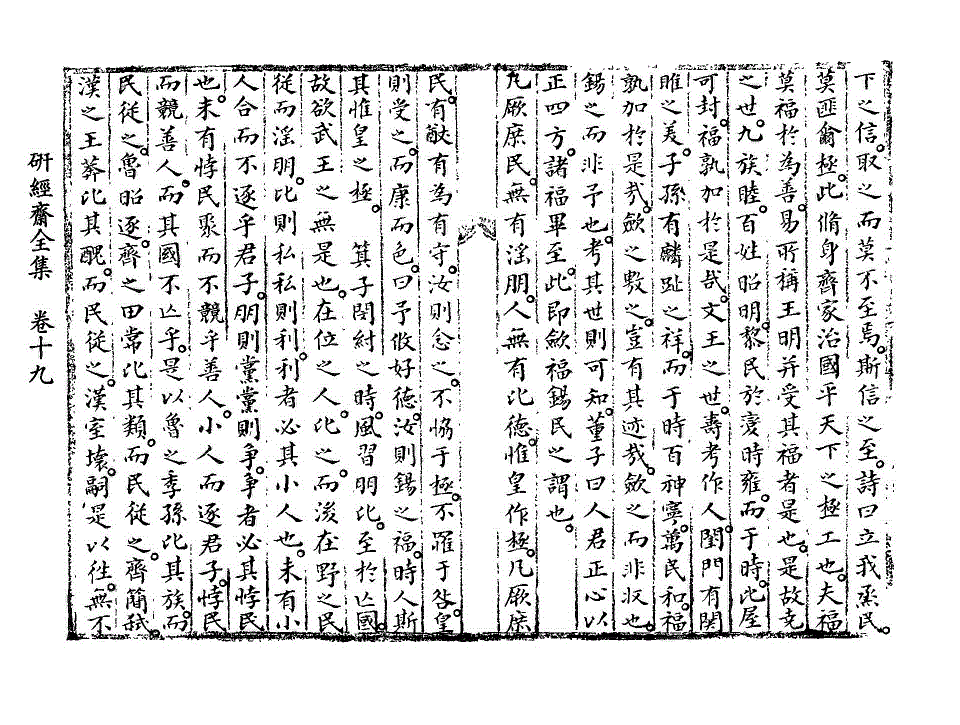 下之信。取之而莫不至焉。斯信之至。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此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极工也。夫福莫福于为善。易所称王明并受其福者是也。是故尧之世。九族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而于时。比屋可封。福孰加于是哉。文王之世。寿考作人。闺门有关雎之美。子孙有麟趾之祥。而于时百神宁。万民和。福孰加于是哉。敛之敷之。岂有其迹哉。敛之而非收也。锡之而非予也。考其世则可知。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诸福毕至。此即敛福锡民之谓也。
下之信。取之而莫不至焉。斯信之至。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此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极工也。夫福莫福于为善。易所称王明并受其福者是也。是故尧之世。九族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而于时。比屋可封。福孰加于是哉。文王之世。寿考作人。闺门有关雎之美。子孙有麟趾之祥。而于时百神宁。万民和。福孰加于是哉。敛之敷之。岂有其迹哉。敛之而非收也。锡之而非予也。考其世则可知。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诸福毕至。此即敛福锡民之谓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箕子闵纣之时。风习朋比。至于亡国。故欲武王之无是也。在位之人。比之。而后在野之民从而淫朋。比则私私则利。利者必其小人也。未有小人合而不逐乎君子。朋则党党则争。争者必其悖民也。未有悖民聚而不竞乎善人。小人而逐君子。悖民而竞善人。而其国不亡乎。是以鲁之季孙比其族。而民从之。鲁昭逐。齐之田常比其类。而民从之。齐简弑。汉之王莽比其丑。而民从之。汉室坏。嗣是以往。无不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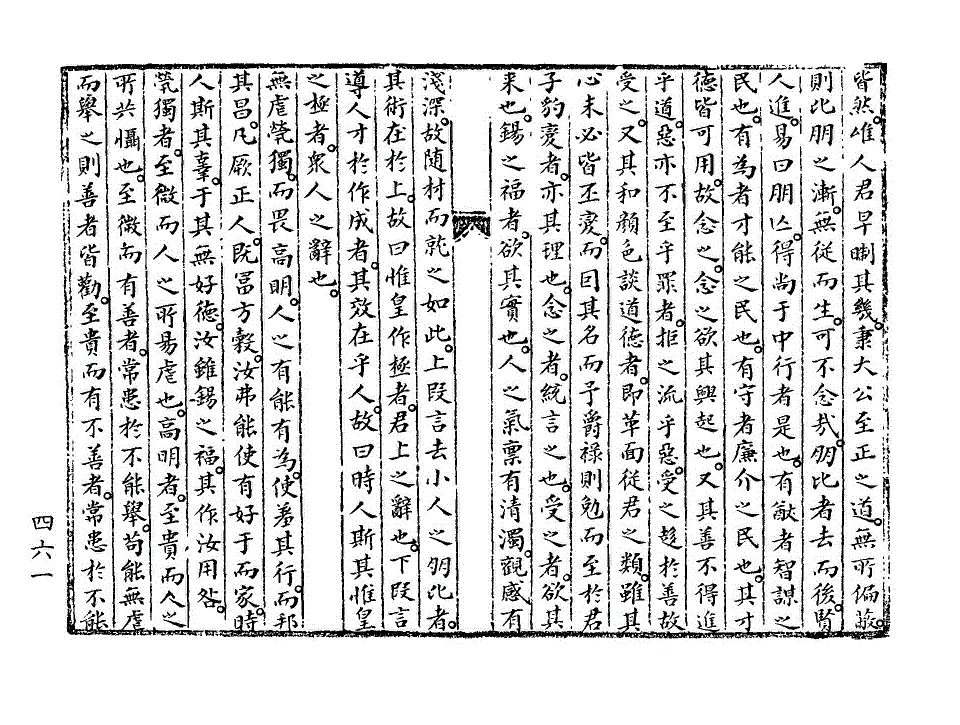 皆然。唯人君早晢其几。秉大公至正之道。无所偏蔽。则比朋之渐。无从而生。可不念哉。朋比者去而后。贤人进。易曰朋亡。得尚于中行者是也。有猷者智谋之民也。有为者才能之民也。有守者廉介之民也。其才德皆可用。故念之。念之欲其兴起也。又其善不得进乎道。恶亦不至乎罪者。拒之流乎恶。受之趍于善故受之。又其和颜色谈道德者。即革面从君之类。虽其心未必皆丕变。而因其名而予爵禄则勉而至于君子豹变者。亦其理也。念之者。统言之也。受之者。欲其来也。锡之福者。欲其实也。人之气禀有清浊。观感有浅深。故随材而就之如此。上段言去小人之朋比者。其术在于上。故曰惟皇作极者。君上之辞也。下段言导人才于作成者。其效在乎人。故曰时人斯其惟皇之极者。众人之辞也。
皆然。唯人君早晢其几。秉大公至正之道。无所偏蔽。则比朋之渐。无从而生。可不念哉。朋比者去而后。贤人进。易曰朋亡。得尚于中行者是也。有猷者智谋之民也。有为者才能之民也。有守者廉介之民也。其才德皆可用。故念之。念之欲其兴起也。又其善不得进乎道。恶亦不至乎罪者。拒之流乎恶。受之趍于善故受之。又其和颜色谈道德者。即革面从君之类。虽其心未必皆丕变。而因其名而予爵禄则勉而至于君子豹变者。亦其理也。念之者。统言之也。受之者。欲其来也。锡之福者。欲其实也。人之气禀有清浊。观感有浅深。故随材而就之如此。上段言去小人之朋比者。其术在于上。故曰惟皇作极者。君上之辞也。下段言导人才于作成者。其效在乎人。故曰时人斯其惟皇之极者。众人之辞也。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茕独者。至微而人之所易虐也。高明者。至贵而人之所共慑也。至微而有善者。常患于不能举。苟能无虐而举之则善者皆劝。至贵而有不善者。常患于不能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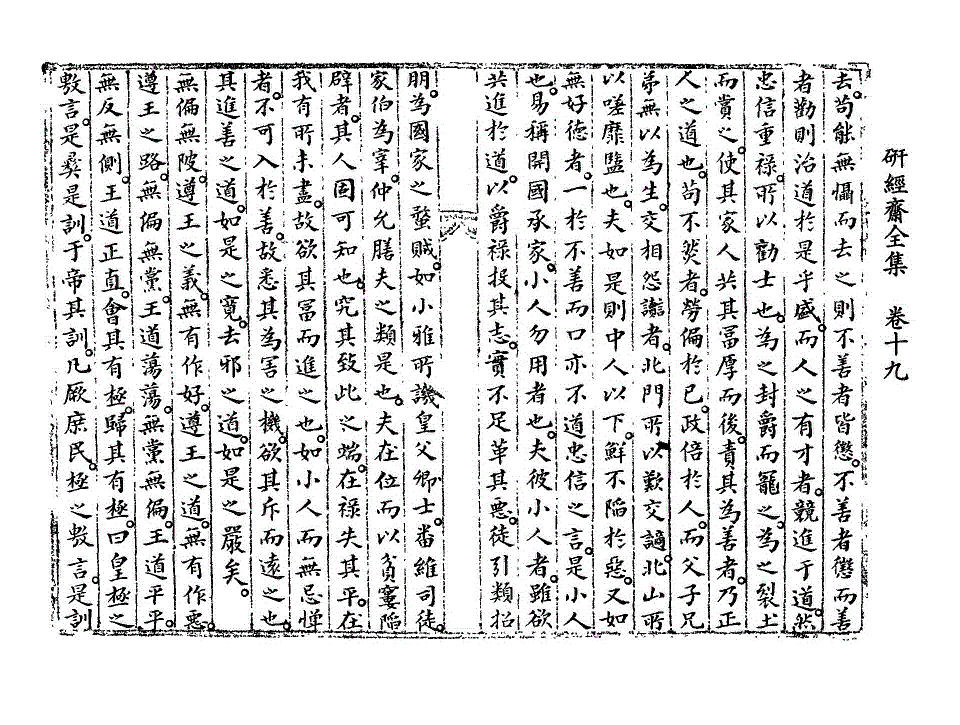 去。苟能无慑而去之则不善者皆惩。不善者惩而善者劝则治道于是乎盛。而人之有才者。竞进于道。然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为之封爵而宠之。为之裂土而赏之。使其家人共其富厚而后。责其为善者。乃正人之道也。苟不然者。劳偏于己。政倍于人。而父子兄弟无以为生。交相怨讟者。北门所以叹交谪。北山所以嗟靡盬也。夫如是则中人以下。鲜不陷于恶。又如无好德者。一于不善而口亦不道忠信之言。是小人也。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者也。夫彼小人者。虽欲共进于道。以爵禄投其志。实不足革其恶。徒引类招朋。为国家之蝥贼。如小雅所讥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之类是也。夫在位而以贫窭陷辟者。其人固可知也。究其致此之端。在禄失其平。在我有所未尽。故欲其富而进之也。如小人而无忌惮者。不可入于善。故悉其为害之机。欲其斥而远之也。其进善之道。如是之宽。去邪之道。如是之严矣。
去。苟能无慑而去之则不善者皆惩。不善者惩而善者劝则治道于是乎盛。而人之有才者。竞进于道。然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为之封爵而宠之。为之裂土而赏之。使其家人共其富厚而后。责其为善者。乃正人之道也。苟不然者。劳偏于己。政倍于人。而父子兄弟无以为生。交相怨讟者。北门所以叹交谪。北山所以嗟靡盬也。夫如是则中人以下。鲜不陷于恶。又如无好德者。一于不善而口亦不道忠信之言。是小人也。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者也。夫彼小人者。虽欲共进于道。以爵禄投其志。实不足革其恶。徒引类招朋。为国家之蝥贼。如小雅所讥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之类是也。夫在位而以贫窭陷辟者。其人固可知也。究其致此之端。在禄失其平。在我有所未尽。故欲其富而进之也。如小人而无忌惮者。不可入于善。故悉其为害之机。欲其斥而远之也。其进善之道。如是之宽。去邪之道。如是之严矣。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2L 页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陂古文作颇。唐玄宗以此句韵独不协。因周易泰卦无平无陂释文。陂亦有颇音。遂改颇为陂。此章忽有韵语。文体与前不同。岂或古之圣训。如乾之四德之说。为夫子所引者欤。盖偏陂好恶。己私之发乎心。偏党反侧。己私之发乎事也。于此六句。并下无字者。戒其陷于私也。遵王之义道路者。劝其之善也。王道荡荡平平正直者。赞其美也。会极归极者。言其效也。曰皇极之敷言以下。上之所以宣下也。凡厥庶民以下。下之所以答上也。夫公卿有位之类。亿兆林丛之众。以至胡越蛮貊之远。不能由于皇极之道者何哉。即一己之私也。圣人所以反复开导。咏叹淫液。备陈其私之可违。善之可乐。荡荡极其远也。平平极其夷也。正直极其坦也。如是而趍于幽昧倾险之径者。岂民之情哉。是故一开其端。导其趍于善则归德也。如川泽之归于海。不至于海则不止。禽兽之归于山。不至于山则不止。此所谓会极归极者也。敷言者何。无偏无陂以下十四句之说也。人主既令臣庶中外。归于皇极之化。而恐其不能久也。常以是戒之曰是常伦也大训也。非我之言。乃上天之言。即书所称戒之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陂古文作颇。唐玄宗以此句韵独不协。因周易泰卦无平无陂释文。陂亦有颇音。遂改颇为陂。此章忽有韵语。文体与前不同。岂或古之圣训。如乾之四德之说。为夫子所引者欤。盖偏陂好恶。己私之发乎心。偏党反侧。己私之发乎事也。于此六句。并下无字者。戒其陷于私也。遵王之义道路者。劝其之善也。王道荡荡平平正直者。赞其美也。会极归极者。言其效也。曰皇极之敷言以下。上之所以宣下也。凡厥庶民以下。下之所以答上也。夫公卿有位之类。亿兆林丛之众。以至胡越蛮貊之远。不能由于皇极之道者何哉。即一己之私也。圣人所以反复开导。咏叹淫液。备陈其私之可违。善之可乐。荡荡极其远也。平平极其夷也。正直极其坦也。如是而趍于幽昧倾险之径者。岂民之情哉。是故一开其端。导其趍于善则归德也。如川泽之归于海。不至于海则不止。禽兽之归于山。不至于山则不止。此所谓会极归极者也。敷言者何。无偏无陂以下十四句之说也。人主既令臣庶中外。归于皇极之化。而恐其不能久也。常以是戒之曰是常伦也大训也。非我之言。乃上天之言。即书所称戒之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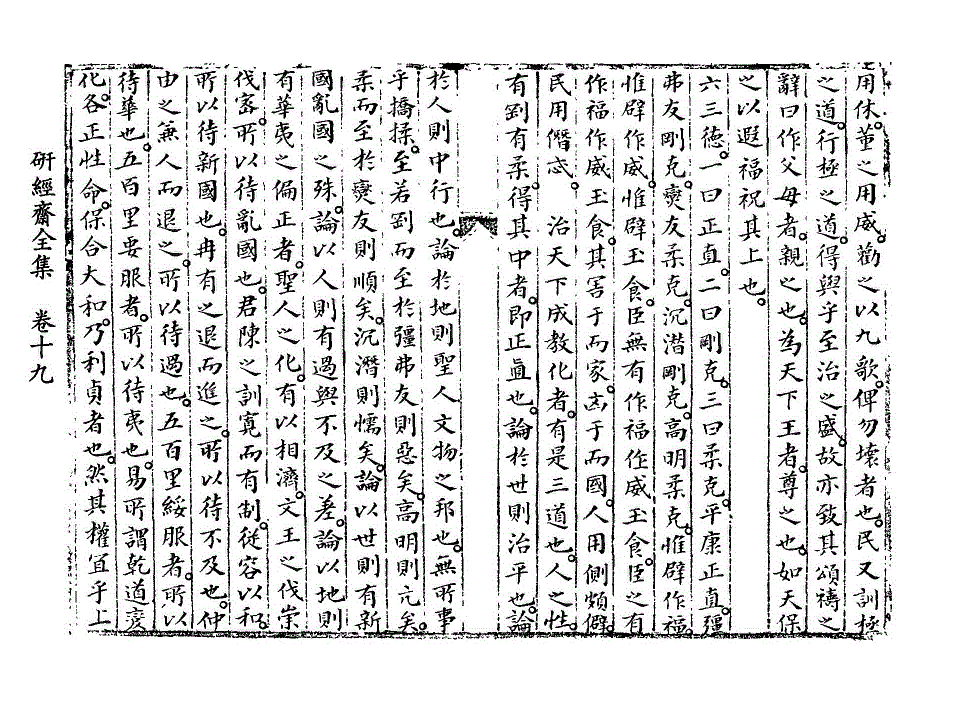 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者也。民又训极之道。行极之道。得与乎至治之盛。故亦致其颂祷之辞曰作父母者。亲之也。为天下王者。尊之也。如天保之以遐福祝其上也。
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者也。民又训极之道。行极之道。得与乎至治之盛。故亦致其颂祷之辞曰作父母者。亲之也。为天下王者。尊之也。如天保之以遐福祝其上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治天下成教化者。有是三道也。人之性。有刚有柔。得其中者。即正直也。论于世则治平也。论于人则中行也。论于地则圣人文物之邦也。无所事乎挢揉。至若刚而至于彊弗友则恶矣。高明则亢矣。柔而至于燮友则顺矣。沉潜则懦矣。论以世则有新国乱国之殊。论以人则有过与不及之差。论以地则有华夷之偏正者。圣人之化。有以相济。文王之伐崇伐密。所以待乱国也。君陈之训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所以待新国也。冉有之退而进之。所以待不及也。仲由之兼人而退之。所以待过也。五百里绥服者。所以待华也。五百里要服者。所以待夷也。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者也。然其权宜乎上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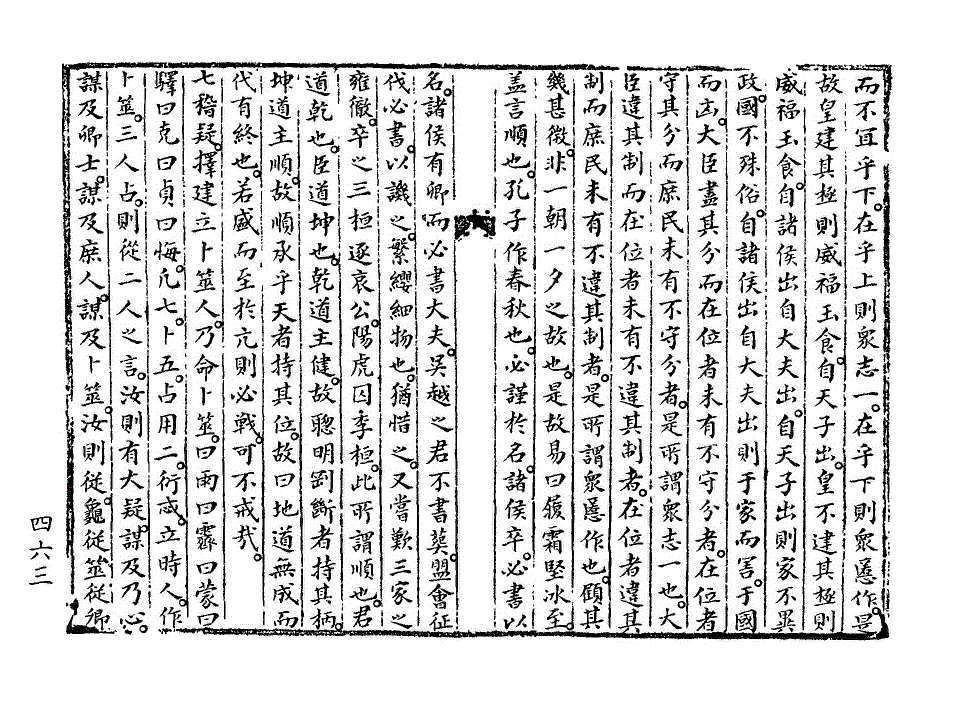 而不宜乎下。在乎上则众志一。在乎下则众慝作。是故皇建其极则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不建其极则威福玉食。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天子出则家不异政。国不殊俗。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则于家而害。于国而凶。大臣尽其分而在位者未有不守分者。在位者守其分而庶民未有不守分者。是所谓众志一也。大臣违其制而在位者未有不违其制者。在位者违其制而庶民未有不违其制者。是所谓众慝作也。顾其几甚微。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故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孔子作春秋也。必谨于名。诸侯卒。必书以名。诸侯有卿而必书大夫。吴越之君不书葬。盟会征伐必书。以讥之。繁缨细物也。犹惜之。又尝叹三家之雍彻。卒之三桓逐哀公。阳虎囚季桓。此所谓顺也。君道乾也。臣道坤也。乾道主健。故聪明刚断者持其柄。坤道主顺。故顺承乎天者持其位。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若盛而至于亢则必战。可不戒哉。
而不宜乎下。在乎上则众志一。在乎下则众慝作。是故皇建其极则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不建其极则威福玉食。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天子出则家不异政。国不殊俗。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则于家而害。于国而凶。大臣尽其分而在位者未有不守分者。在位者守其分而庶民未有不守分者。是所谓众志一也。大臣违其制而在位者未有不违其制者。在位者违其制而庶民未有不违其制者。是所谓众慝作也。顾其几甚微。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故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孔子作春秋也。必谨于名。诸侯卒。必书以名。诸侯有卿而必书大夫。吴越之君不书葬。盟会征伐必书。以讥之。繁缨细物也。犹惜之。又尝叹三家之雍彻。卒之三桓逐哀公。阳虎囚季桓。此所谓顺也。君道乾也。臣道坤也。乾道主健。故聪明刚断者持其柄。坤道主顺。故顺承乎天者持其位。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若盛而至于亢则必战。可不戒哉。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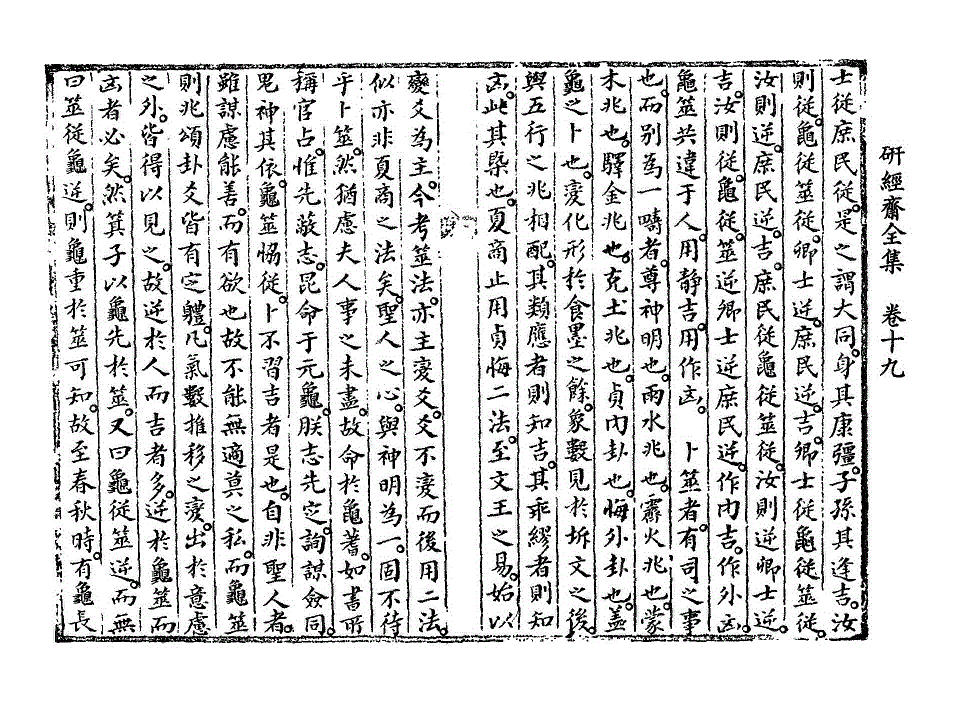 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彊。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卜筮者。有司之事也。而别为一畴者。尊神明也。雨水兆也。霁火兆也。蒙木兆也。驿金兆也。克土兆也。贞内卦也。悔外卦也。盖龟之卜也。变化形于食墨之馀。象数见于坼文之后。与五行之兆相配。其类应者则知吉。其乖缪者则知凶。此其槩也。夏商止用贞悔二法。至文王之易。始以变爻为主。今考筮法。亦主变爻。爻不变而后用二法。似亦非夏商之法矣。圣人之心。与神明为一。固不待乎卜筮。然犹虑夫人事之未尽。故命于龟蓍。如书所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者是也。自非圣人者。虽谋虑能善。而有欲也故不能无适莫之私。而龟筮则兆颂卦爻皆有定体。凡气数推移之变。出于意虑之外。皆得以见之。故逆于人而吉者多。逆于龟筮而凶者必矣。然箕子以龟先于筮。又曰龟从筮逆。而无曰筮从龟逆。则龟重于筮可知。故至春秋时。有龟长
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彊。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卜筮者。有司之事也。而别为一畴者。尊神明也。雨水兆也。霁火兆也。蒙木兆也。驿金兆也。克土兆也。贞内卦也。悔外卦也。盖龟之卜也。变化形于食墨之馀。象数见于坼文之后。与五行之兆相配。其类应者则知吉。其乖缪者则知凶。此其槩也。夏商止用贞悔二法。至文王之易。始以变爻为主。今考筮法。亦主变爻。爻不变而后用二法。似亦非夏商之法矣。圣人之心。与神明为一。固不待乎卜筮。然犹虑夫人事之未尽。故命于龟蓍。如书所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者是也。自非圣人者。虽谋虑能善。而有欲也故不能无适莫之私。而龟筮则兆颂卦爻皆有定体。凡气数推移之变。出于意虑之外。皆得以见之。故逆于人而吉者多。逆于龟筮而凶者必矣。然箕子以龟先于筮。又曰龟从筮逆。而无曰筮从龟逆。则龟重于筮可知。故至春秋时。有龟长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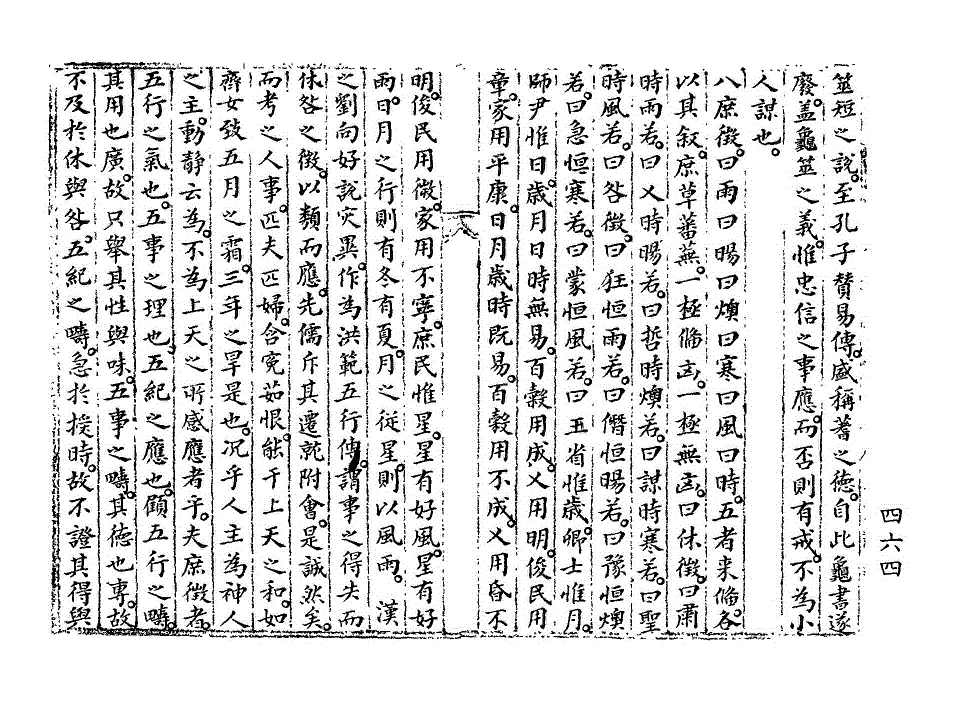 筮短之说。至孔子赞易传。盛称蓍之德。自此龟书遂废。盖龟筮之义。惟忠信之事应。而否则有戒。不为小人谋也。
筮短之说。至孔子赞易传。盛称蓍之德。自此龟书遂废。盖龟筮之义。惟忠信之事应。而否则有戒。不为小人谋也。八庶徵。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芜。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汉之刘向好说灾异。作为洪范五行传。谓事之得失而休咎之徵。以类而应。先儒斥其迁就附会。是诚然矣。而考之人事。匹夫匹妇。含冤茹恨。能干上天之和。如齐女致五月之霜。三年之旱是也。况乎人主为神人之主。动静云为。不为上天之所感应者乎。夫庶徵者。五行之气也。五事之理也。五纪之应也。顾五行之畴。其用也广。故只举其性与味。五事之畴。其德也专。故不及于休与咎。五纪之畴。急于授时。故不證其得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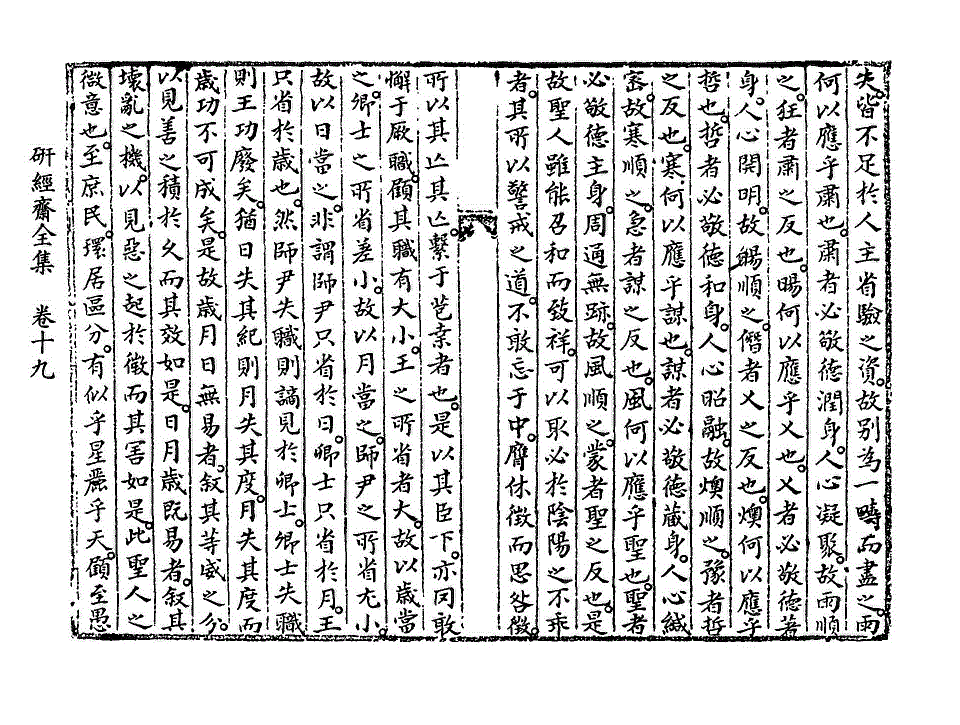 失。皆不足于人主省验之资。故别为一畴而尽之。雨何以应乎肃也。肃者必敬德润身。人心凝聚。故雨顺之。狂者肃之反也。旸何以应乎乂也。乂者必敬德著身。人心开明。故旸顺之。僭者乂之反也。燠何以应乎哲也。哲者必敬德和身。人心昭融。故燠顺之。豫者哲之反也。寒何以应乎谋也。谋者必敬德藏身。人心缄密。故寒顺之。急者谋之反也。风何以应乎圣也。圣者必敬德主身。周通无迹。故风顺之。蒙者圣之反也。是故圣人虽能召和而致祥。可以取必于阴阳之不乖者。其所以警戒之道。不敢忘于中。膺休徵而思咎徵。所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也。是以其臣下。亦罔敢懈于厥职。顾其职有大小。王之所省者大。故以岁当之。卿士之所省差小。故以月当之。师尹之所省尤小。故以日当之。非谓师尹只省于日。卿士只省于月。王只省于岁也。然师尹失职则谪见于卿士。卿士失职则王功废矣。犹日失其纪则月失其度。月失其度而岁功不可成矣。是故岁月日无易者。叙其等威之分。以见善之积于久而其效如是。日月岁既易者。叙其坏乱之机。以见恶之起于微而其害如是。此圣人之微意也。至庶民。环居区分。有似乎星丽乎天。顾至愚
失。皆不足于人主省验之资。故别为一畴而尽之。雨何以应乎肃也。肃者必敬德润身。人心凝聚。故雨顺之。狂者肃之反也。旸何以应乎乂也。乂者必敬德著身。人心开明。故旸顺之。僭者乂之反也。燠何以应乎哲也。哲者必敬德和身。人心昭融。故燠顺之。豫者哲之反也。寒何以应乎谋也。谋者必敬德藏身。人心缄密。故寒顺之。急者谋之反也。风何以应乎圣也。圣者必敬德主身。周通无迹。故风顺之。蒙者圣之反也。是故圣人虽能召和而致祥。可以取必于阴阳之不乖者。其所以警戒之道。不敢忘于中。膺休徵而思咎徵。所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也。是以其臣下。亦罔敢懈于厥职。顾其职有大小。王之所省者大。故以岁当之。卿士之所省差小。故以月当之。师尹之所省尤小。故以日当之。非谓师尹只省于日。卿士只省于月。王只省于岁也。然师尹失职则谪见于卿士。卿士失职则王功废矣。犹日失其纪则月失其度。月失其度而岁功不可成矣。是故岁月日无易者。叙其等威之分。以见善之积于久而其效如是。日月岁既易者。叙其坏乱之机。以见恶之起于微而其害如是。此圣人之微意也。至庶民。环居区分。有似乎星丽乎天。顾至愚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5L 页
 而神。故有所好。如好风之星。好雨之星。所好者何也。善者从之。恶者违之。上亦徇其所好。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愚者教之。俾安其所。此卿士师尹所以建官设职者也。惟其上操其权。下行其职。故各有常度。如日月之行冬夏。皆循其道。若或失其道而东北入于箕则多风。西南入于毕则多雨。喻循常则民情顺。变常则民情拂。可不戒哉。言月从星而不言口从星何也。月从日者也。
而神。故有所好。如好风之星。好雨之星。所好者何也。善者从之。恶者违之。上亦徇其所好。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愚者教之。俾安其所。此卿士师尹所以建官设职者也。惟其上操其权。下行其职。故各有常度。如日月之行冬夏。皆循其道。若或失其道而东北入于箕则多风。西南入于毕则多雨。喻循常则民情顺。变常则民情拂。可不戒哉。言月从星而不言口从星何也。月从日者也。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拆。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人君建皇极于上而福萃焉。传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者是也。君亦以是导其民。使之趍福而避极。福极者天之所命而君之所得与夺也。惟其无一毫之私。故与夺得其正而民皆从之。养而不伤。故民亦摄其生而寿。厚而不夺。故民亦勤其业而富。扶而不危。故民亦节其力而康宁。教而不违。故民亦趍于善而攸好德。生而不困。故民皆安其性而考终命。此建极之极功也。然养而不伤。民或短折焉。厚而不夺。民或贫焉。扶而不危。民或忧且疾焉。教而不违。民或恶且弱焉。生而不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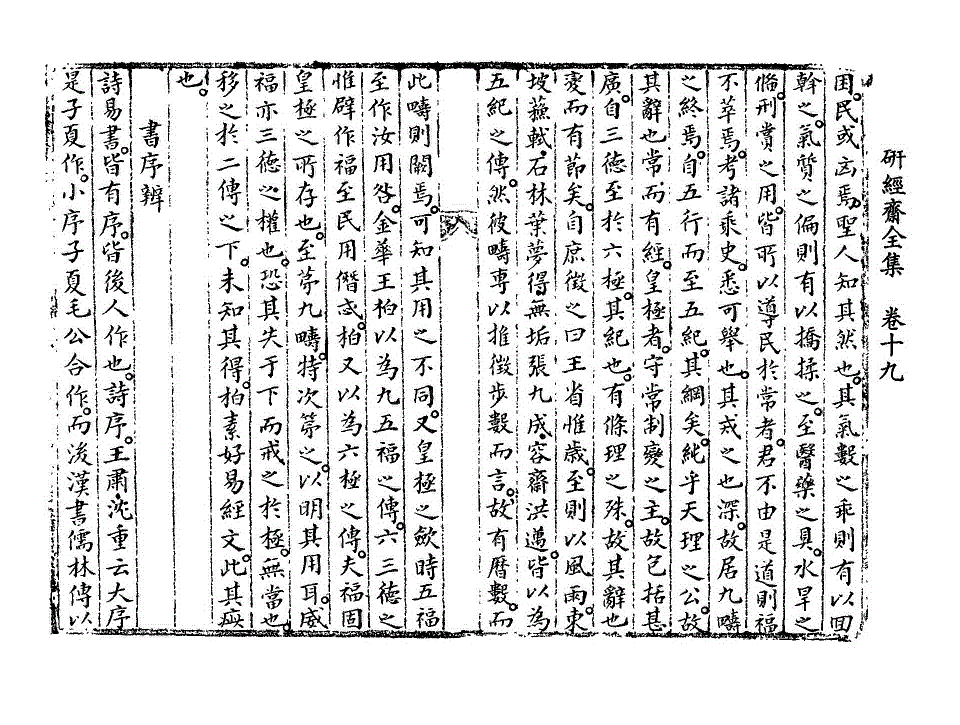 困。民或凶焉。圣人知其然也。其气数之乖则有以回斡之。气质之偏则有以挢揉之。至医药之具。水旱之备。刑赏之用。皆所以导民于常者。君不由是道则福不萃焉。考诸乘史。悉可举也。其戒之也深。故居九畴之终焉。自五行而至五纪。其纲矣。纯乎天理之公。故其辞也常而有经。皇极者。守常制变之主。故包括甚广。自三德至于六极。其纪也。有条理之殊。故其辞也变而有节矣。自庶徵之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东坡苏轼,石林叶梦得,无垢张九成,容斋洪迈。皆以为五纪之传。然彼畴专以推徵步数而言。故有历数。而此畴则阙焉。可知其用之不同。又皇极之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金华王柏以为九五福之传。六三德之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柏又以为六极之传。夫福固皇极之所存也。至第九畴。特次第之。以明其用耳。威福亦三德之权也。恐其失于下而戒之于极。无当也。移之于二传之下。未知其得。柏素好易经文。此其疵也。
困。民或凶焉。圣人知其然也。其气数之乖则有以回斡之。气质之偏则有以挢揉之。至医药之具。水旱之备。刑赏之用。皆所以导民于常者。君不由是道则福不萃焉。考诸乘史。悉可举也。其戒之也深。故居九畴之终焉。自五行而至五纪。其纲矣。纯乎天理之公。故其辞也常而有经。皇极者。守常制变之主。故包括甚广。自三德至于六极。其纪也。有条理之殊。故其辞也变而有节矣。自庶徵之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东坡苏轼,石林叶梦得,无垢张九成,容斋洪迈。皆以为五纪之传。然彼畴专以推徵步数而言。故有历数。而此畴则阙焉。可知其用之不同。又皇极之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金华王柏以为九五福之传。六三德之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柏又以为六极之传。夫福固皇极之所存也。至第九畴。特次第之。以明其用耳。威福亦三德之权也。恐其失于下而戒之于极。无当也。移之于二传之下。未知其得。柏素好易经文。此其疵也。书序辨
诗易书。皆有序。皆后人作也。诗序。王肃,沈重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而后汉书儒林传以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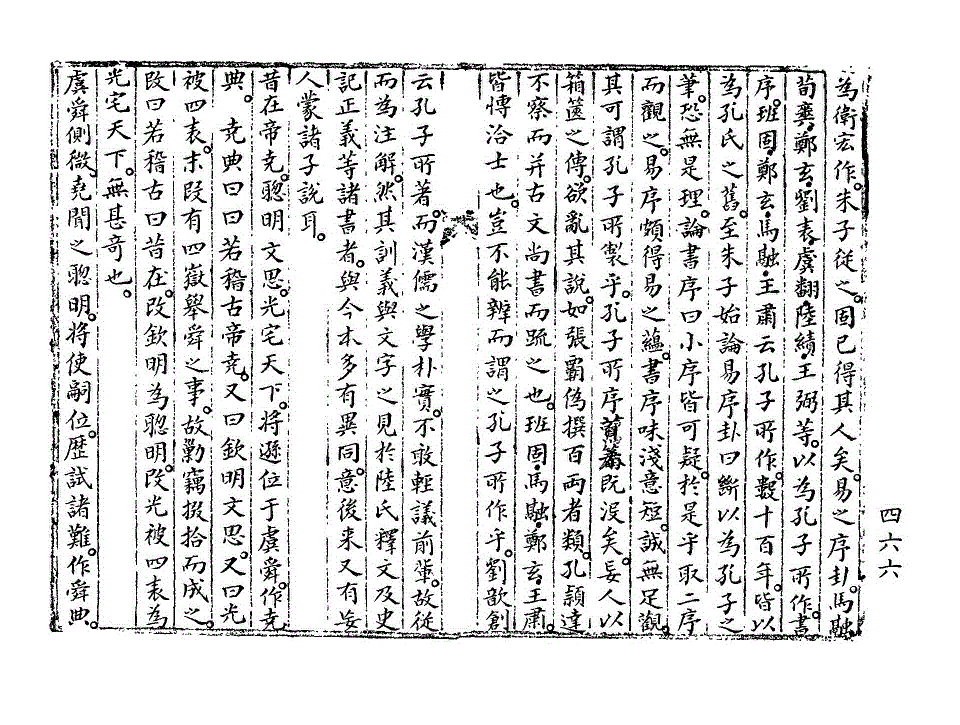 为卫宏作。朱子从之。固已得其人矣。易之序卦。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王弼等。以为孔子所作。书序。班固,郑玄,马融,王肃云孔子所作。数十百年。皆以为孔氏之旧。至朱子始论易序卦曰断以为孔子之笔。恐无是理。论书序曰小序皆可疑。于是乎取二序而观之。易序颇得易之蕴。书序味浅意短。诚无足观。其可谓孔子所制乎。孔子所序首篇既没矣。妄人以箱箧之传。欲乱其说。如张霸伪撰百两者类。孔颖达不察而并古文尚书而疏之也。班固,马融,郑玄,王肃。皆博洽士也。岂不能辨而谓之孔子所作乎。刘歆创云孔子所著。而汉儒之学朴实。不敢轻议前辈。故从而为注解。然其训义与文字之见于陆氏释文及史记正义等诸书者。与今本多有异同。意后来又有妄人蒙诸子说耳。
为卫宏作。朱子从之。固已得其人矣。易之序卦。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王弼等。以为孔子所作。书序。班固,郑玄,马融,王肃云孔子所作。数十百年。皆以为孔氏之旧。至朱子始论易序卦曰断以为孔子之笔。恐无是理。论书序曰小序皆可疑。于是乎取二序而观之。易序颇得易之蕴。书序味浅意短。诚无足观。其可谓孔子所制乎。孔子所序首篇既没矣。妄人以箱箧之传。欲乱其说。如张霸伪撰百两者类。孔颖达不察而并古文尚书而疏之也。班固,马融,郑玄,王肃。皆博洽士也。岂不能辨而谓之孔子所作乎。刘歆创云孔子所著。而汉儒之学朴实。不敢轻议前辈。故从而为注解。然其训义与文字之见于陆氏释文及史记正义等诸书者。与今本多有异同。意后来又有妄人蒙诸子说耳。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位于虞舜。作尧典。 尧典曰曰若稽古帝尧。又曰钦明文思。又曰光被四表。末段有四岳举舜之事。故剿窃掇拾而成之。改曰若稽古曰昔在。改钦明为聪明。改光被四表为光宅天下。无甚奇也。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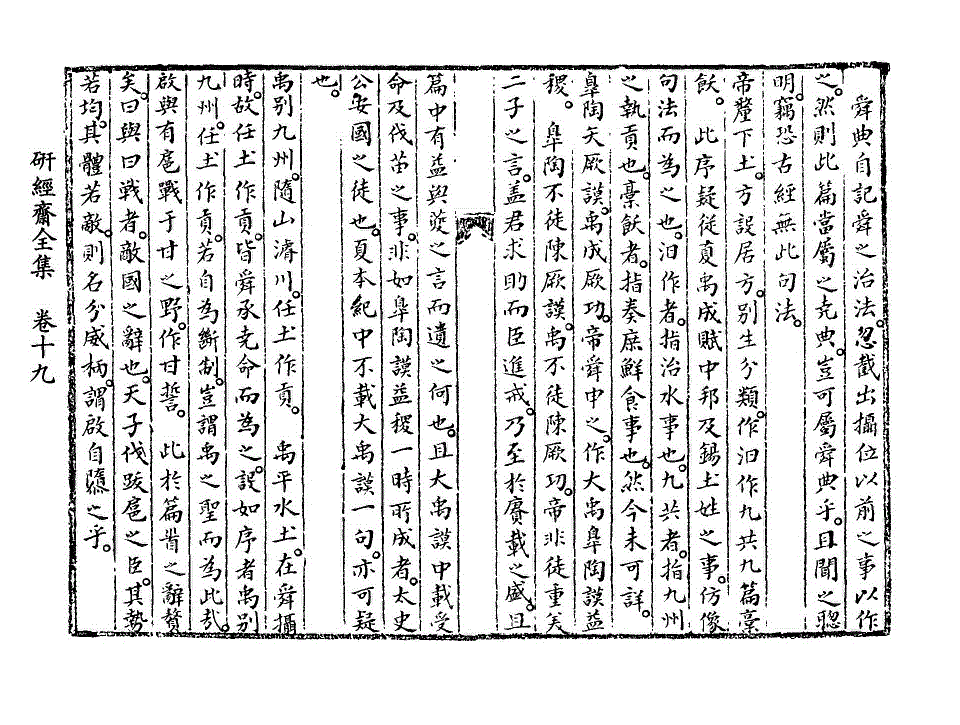 舜典自记舜之治法。忽截出摄位以前之事以作之。然则此篇当属之尧典。岂可属舜典乎。且闻之聪明。窃恐古经无此句法。
舜典自记舜之治法。忽截出摄位以前之事以作之。然则此篇当属之尧典。岂可属舜典乎。且闻之聪明。窃恐古经无此句法。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 此序疑从夏禹成赋中邦及锡土姓之事。仿像句法而为之也。汩作者。指治水事也。九共者。指九州之执贡也。槁饫者。指奏庶鲜食事也。然今未可详。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皋陶不徒陈厥谟。禹不徒陈厥功。帝非徒重美二子之言。盖君求助而臣进戒。乃至于赓载之盛。且篇中有益与夔之言而遗之何也。且大禹谟中载受命及伐苗之事。非如皋陶谟益稷一时所成者。太史公,安国之徒也。夏本纪中不载大禹谟一句。亦可疑也。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平水土。在舜摄时。故任土作贡。皆舜承尧命而为之。设如序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若自为断制。岂谓禹之圣而为此哉。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于篇首之辞赘矣。曰与曰战者。敌国之辞也。天子伐跋扈之臣。其势若均。其体若敌。则名分威柄。谓启自隳之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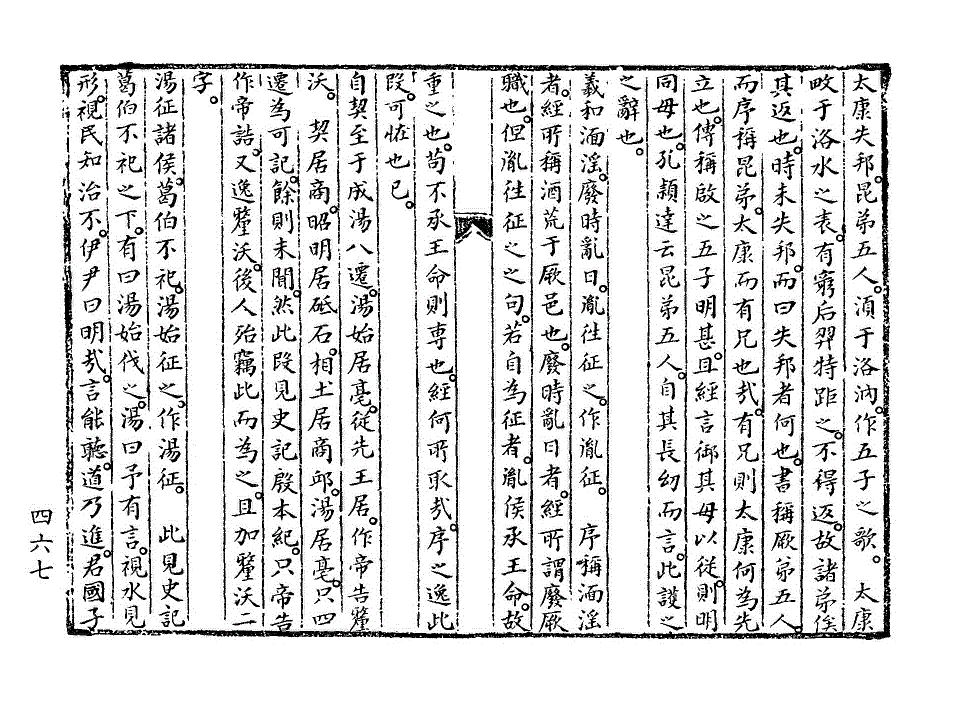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畋于洛水之表。有穷后羿特距之。不得返。故诸弟俟其返也。时未失邦。而曰失邦者何也。书称厥弟五人。而序称昆弟。太康而有兄也哉。有兄则太康何为先立也。传称启之五子明甚。且经言御其母以从。则明同母也。孔颖达云昆弟五人。自其长幼而言。此护之之辞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畋于洛水之表。有穷后羿特距之。不得返。故诸弟俟其返也。时未失邦。而曰失邦者何也。书称厥弟五人。而序称昆弟。太康而有兄也哉。有兄则太康何为先立也。传称启之五子明甚。且经言御其母以从。则明同母也。孔颖达云昆弟五人。自其长幼而言。此护之之辞也。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序称湎淫者。经所称酒荒于厥邑也。废时乱日者。经所谓废厥职也。但胤往征之之句。若自为征者。胤侯承王命。故重之也。苟不承王命则专也。经何所取哉。序之逸此段。可怪也已。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汤居亳。只四迁为可记。馀则未闻。然此段见史记殷本纪。只帝告作帝诰。又逸釐沃。后人殆窃此而为之。且加釐沃二字。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此见史记葛伯不祀之下。有曰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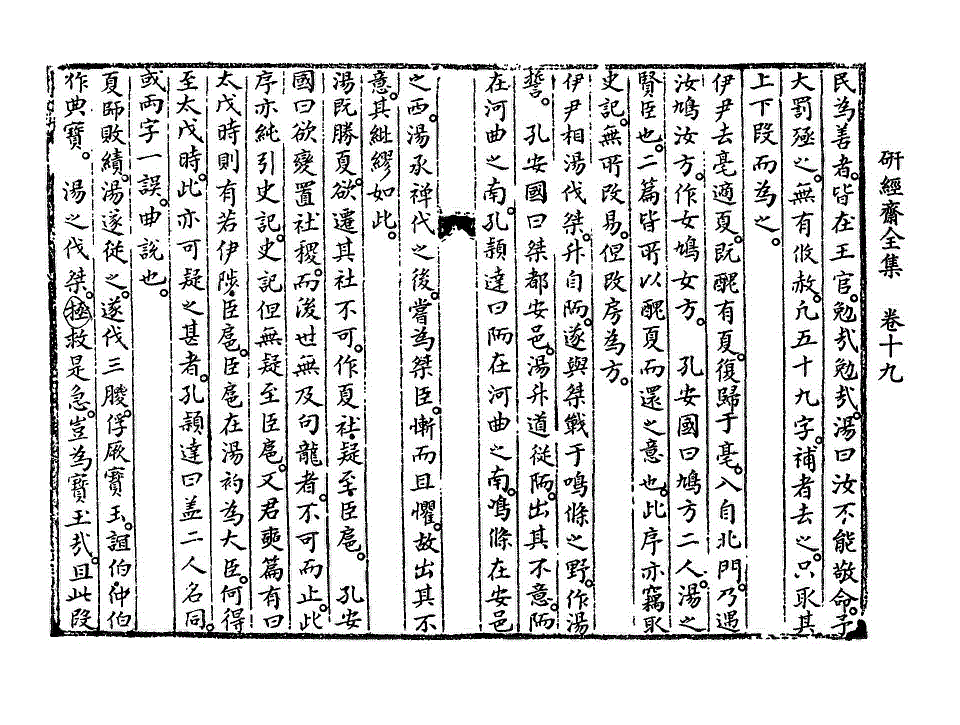 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凡五十九字。补者去之。只取其上下段而为之。
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凡五十九字。补者去之。只取其上下段而为之。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女鸠女方。 孔安国曰鸠方二人。汤之贤臣也。二篇皆所以丑夏而还之意也。此序亦窃取史记。无所改易。但改房为方。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孔安国曰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孔颖达曰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汤承禅代之后。尝为桀臣。惭而且惧。故出其不意。其纰缪如此。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国曰欲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不可而止。此序亦纯引史记。史记但无疑至臣扈。又君奭篇有曰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臣扈在汤初为大臣。何得至太戊时。此亦可疑之甚者。孔颖达曰盖二人名同。或两字一误。曲说也。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汤之伐桀。拯救是急。岂为宝玉哉。且此段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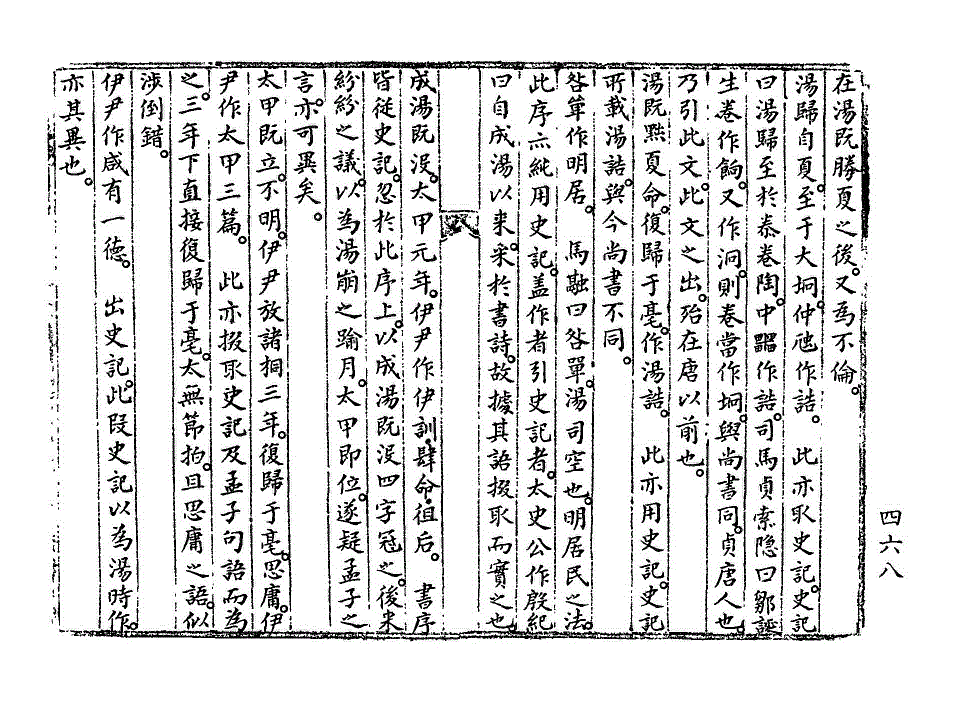 在汤既胜夏之后。又为不伦。
在汤既胜夏之后。又为不伦。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此亦取史记。史记曰汤归至于泰卷陶。中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此亦用史记。史记所载汤诰。与今尚书不同。
咎单作明居。 马融曰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此序亦纯用史记。盖作者引史记者。太史公作殷纪曰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故据其语掇取而实之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书序皆从史记。忽于此序上。以成汤既没四字冠之。后来纷纷之议。以为汤崩之踰月。太甲即位。遂疑孟子之言。亦可异矣。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此亦掇取史记及孟子句语而为之。三年下直接复归于亳。太无节拍。且思庸之语。似涉倒错。
伊尹作咸有一德。 出史记。此段史记以为汤时作。亦其异也。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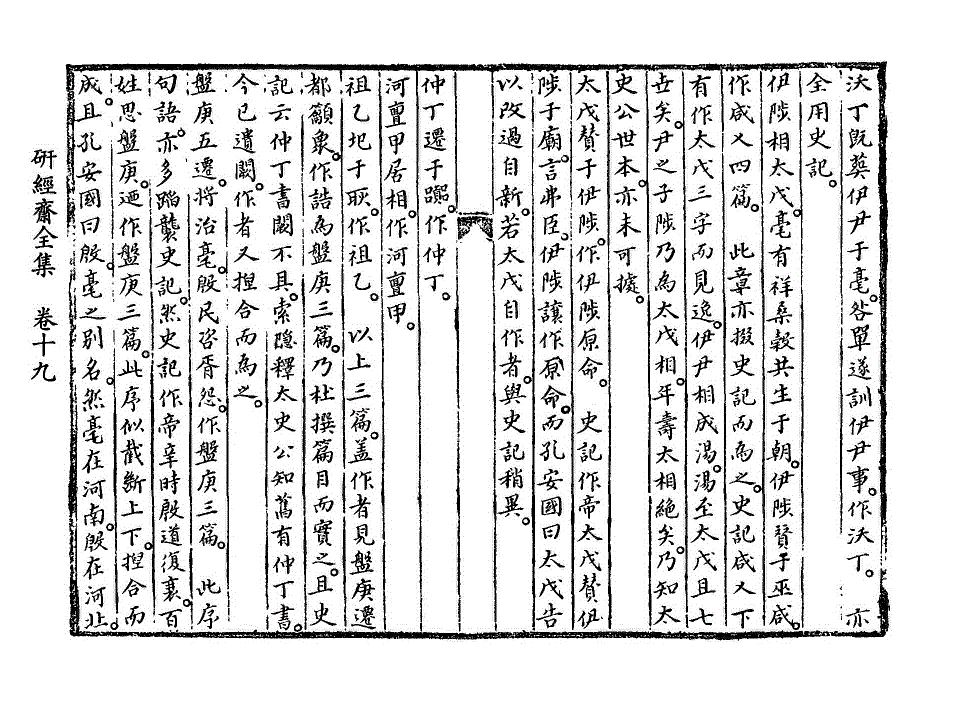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亦全用史记。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亦全用史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此章亦掇史记而为之。史记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而见逸。伊尹相成汤。汤至太戊且七世矣。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年寿太相绝矣。乃知太史公世本。亦未可据。
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记作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而孔安国曰太戊告以改过自新。若太戊自作者。与史记稍异。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以上三篇。盖作者见盘庚迁都吁众。作诰为盘庚三篇。乃杜撰篇目而实之。且史记云仲丁书阙不具。索隐释太史公知旧有仲丁书。今已遗阙。作者又捏合而为之。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此序句语。亦多蹈袭史记。然史记作帝辛时殷道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此序似截断上下。捏合而成。且孔安国曰殷。亳之别名。然亳在河南。殷在河北。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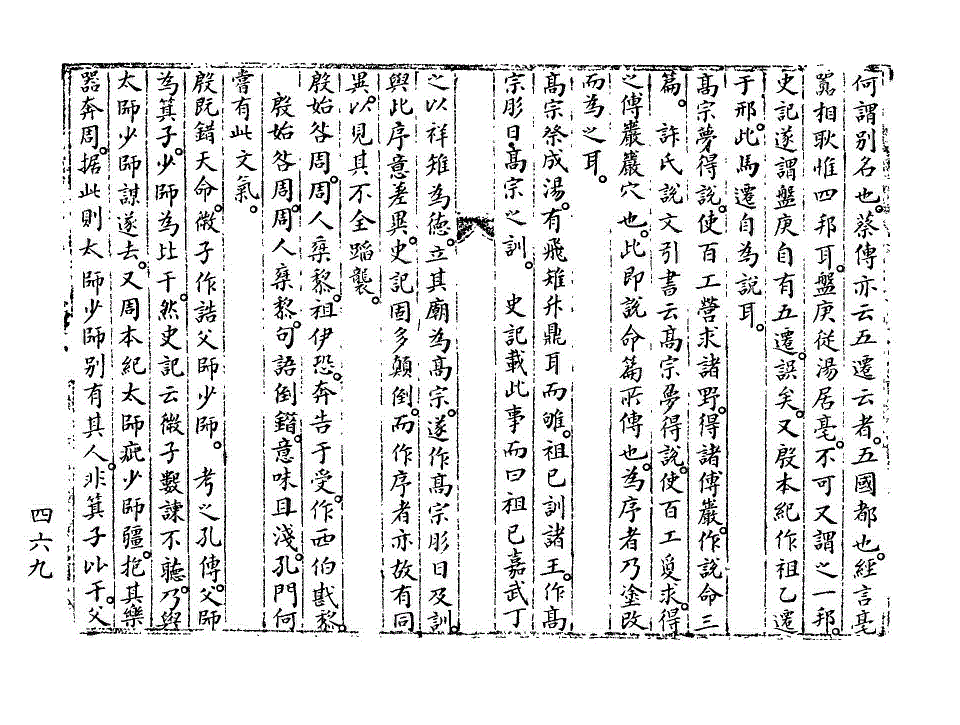 何谓别名也。蔡传亦云五迁云者。五国都也。经言亳嚣相耿惟四邦耳。盘庚从汤居亳。不可又谓之一邦。史记遂谓盘庚自有五迁。误矣。又殷本纪作祖乙迁于邢。此马迁自为说耳。
何谓别名也。蔡传亦云五迁云者。五国都也。经言亳嚣相耿惟四邦耳。盘庚从汤居亳。不可又谓之一邦。史记遂谓盘庚自有五迁。误矣。又殷本纪作祖乙迁于邢。此马迁自为说耳。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许氏说文引书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岩岩穴也。此即说命篇所传也。为序者乃涂改而为之耳。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史记载此事而曰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与此序意差异。史记固多颠倒。而作序者亦故有同异。以见其不全蹈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句语倒错。意味且浅。孔门何尝有此文气。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 考之孔传。父师为箕子。少师为比干。然史记云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又周本纪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奔周。据此则太师少师别有其人。非箕子比干。父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0H 页
 师似指太师。
师似指太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孔颖达云一月戊午。乃作誓月日也。经言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以此知一月戊午。乃十三年戊午。序乃以一月接十一年者。武王以十一年观兵。至而即还。故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十三年春正而言一月。使互相足也。然经既言十三年则十一年者误也。孔颖达诚疑之。顾护安国说。而其言窘遁。不成事理。至朱子又引洪范篇十有三祀之文以證之。蔡氏集传及广汉张氏,仁山金氏皆从之。经旨始明。然伏生大传,史记,太初历,邵子皇极经世。皆作十一年。不可专咎序误。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此剽窃礼记孟子史记语而成。盖古所传也。但改虎贲三千为虎贲三百。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归兽。语似古而实肤浅。孔安国传为武成。记殷家政教善事以为法。篇中何尝举殷一句语也。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洪范之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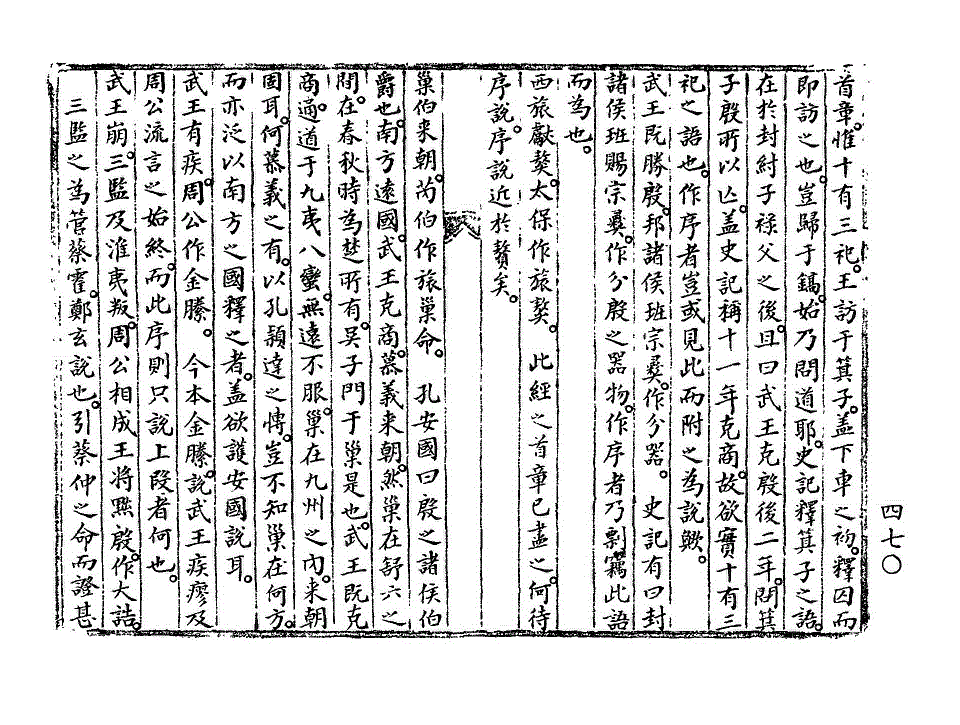 首章。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盖下车之初。释囚而即访之也。岂归于镐。始乃问道耶。史记释箕子之语。在于封纣子禄父之后。且曰武王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盖史记称十一年克商。故欲实十有三祀之语也。作序者岂或见此而附之为说欤。
首章。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盖下车之初。释囚而即访之也。岂归于镐。始乃问道耶。史记释箕子之语。在于封纣子禄父之后。且曰武王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盖史记称十一年克商。故欲实十有三祀之语也。作序者岂或见此而附之为说欤。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记有曰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作序者乃剽窃此语而为也。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 此经之首章已尽之。何待序说。序说近于赘矣。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孔安国曰殷之诸侯伯爵也。南方远国。武王克商。慕义来朝。然巢在舒六之间。在春秋时为楚所有。吴子门于巢是也。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无远不服。巢在九州之内。来朝固耳。何慕义之有。以孔颖达之博。岂不知巢在何方。而亦泛以南方之国释之者。盖欲护安国说耳。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今本金縢。说武王疾瘳及周公流言之始终。而此序则只说上段者何也。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三监之为管蔡霍。郑玄说也。引蔡仲之命而證甚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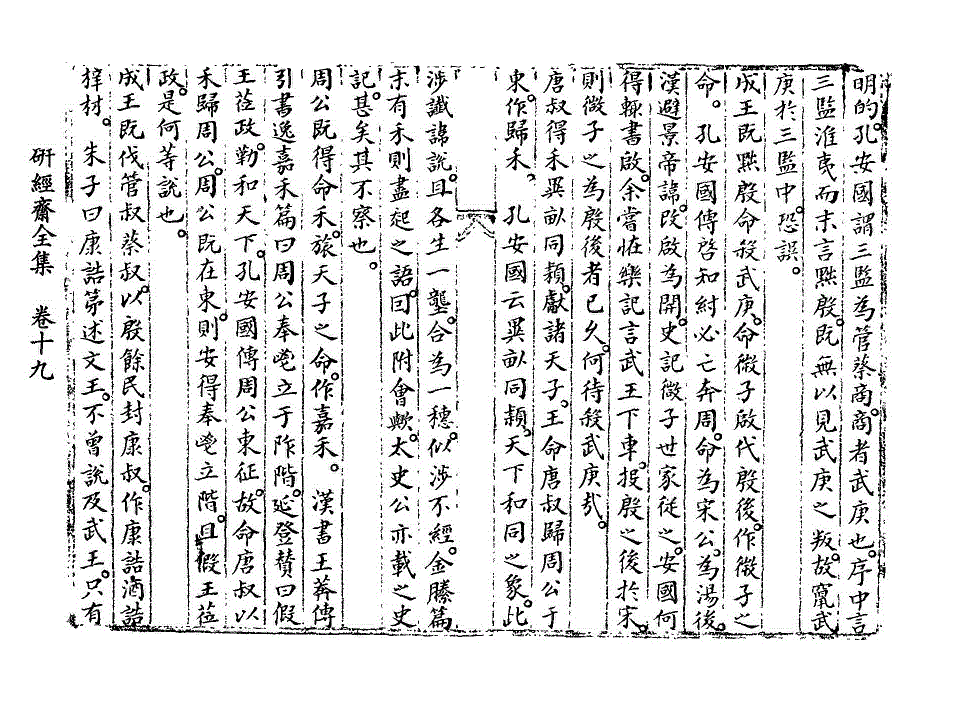 明的。孔安国谓三监为管蔡商。商者武庚也。序中言三监淮夷而末言黜殷。既无以见武庚之叛。故窜武庚于三监中。恐误。
明的。孔安国谓三监为管蔡商。商者武庚也。序中言三监淮夷而末言黜殷。既无以见武庚之叛。故窜武庚于三监中。恐误。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 孔安国传启知纣必亡奔周。命为宋公。为汤后。汉避景帝讳。改启为开。史记微子世家从之。安国何得辄书启。余尝怪乐记言武王下车。投殷之后于宋。则微子之为殷后者已久。何待杀武庚哉。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孔安国云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此涉谶讳说。且各生一垄。合为一穗。似涉不经。金縢篇末有禾则尽起之语。因此附会欤。太史公亦载之史记。甚矣其不察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汉书王莽传引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勒和天下。孔安国传周公东征。故命唐叔以禾归周公。周公既在东。则安得奉鬯立阶。且假王莅政。是何等说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朱子曰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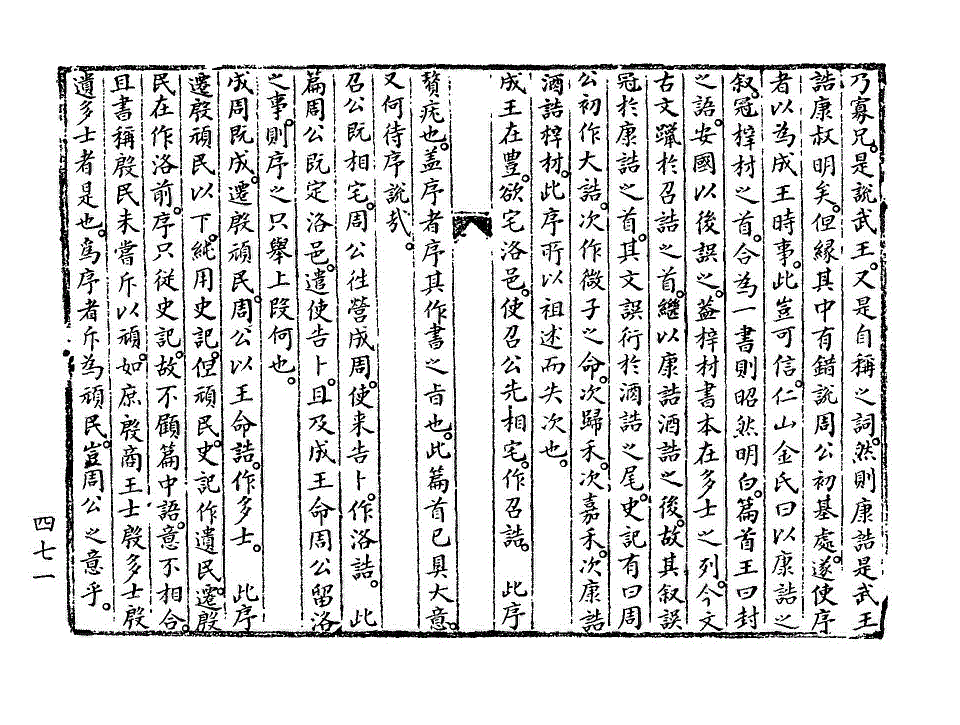 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仁山金氏曰以康诰之叙。冠梓材之首。合为一书则昭然明白。篇首王曰封之语。安国以后误之。盖梓材书本在多士之列。今文古文躐于召诰之首。继以康诰酒诰之后。故其叙误冠于康诰之首。其文误衍于酒诰之尾。史记有曰周公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此序所以祖述而失次也。
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仁山金氏曰以康诰之叙。冠梓材之首。合为一书则昭然明白。篇首王曰封之语。安国以后误之。盖梓材书本在多士之列。今文古文躐于召诰之首。继以康诰酒诰之后。故其叙误冠于康诰之首。其文误衍于酒诰之尾。史记有曰周公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此序所以祖述而失次也。成王在礼。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此序赘疣也。盖序者序其作书之旨也。此篇首已具大意。又何待序说哉。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此篇周公既定洛邑。遣使告卜。且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则序之只举上段何也。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此序迁殷顽民以下。纯用史记。但顽民。史记作遗民。迁殷民在作洛前。序只从史记。故不顾篇中语。意不相合。且书称殷民未尝斥以顽。如庶殷商王士殷多士殷遗多士者是也。为序者斥为顽民。岂周公之意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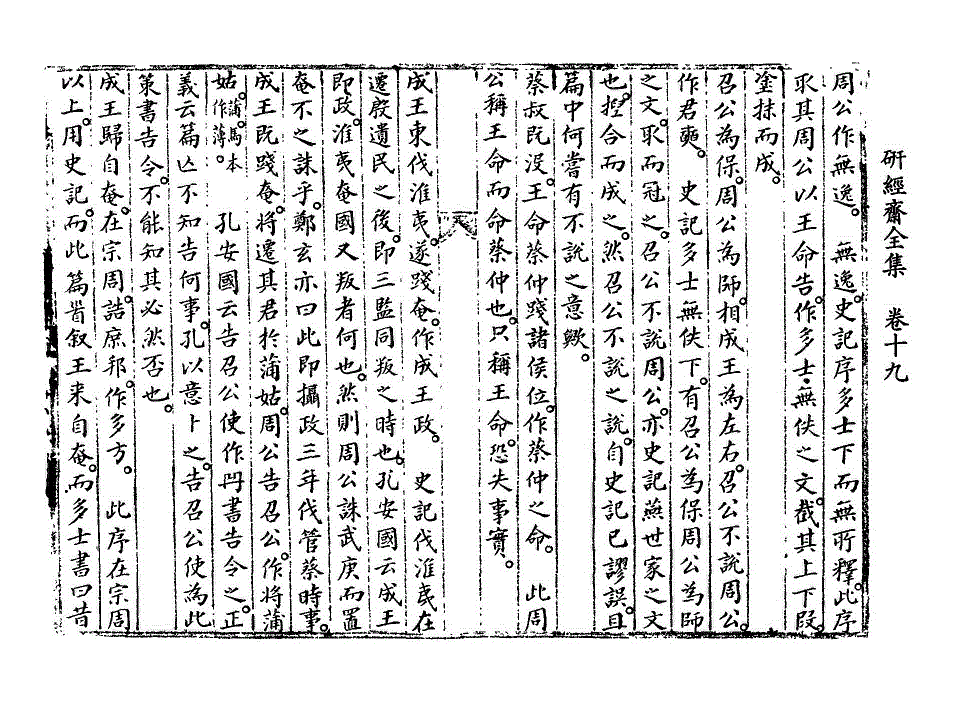 周公作无逸。 无逸。史记序多士下而无所释。此序取其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之文。截其上下段。涂抹而成。
周公作无逸。 无逸。史记序多士下而无所释。此序取其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之文。截其上下段。涂抹而成。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 史记多士无佚下。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之文。取而冠之。召公不说周公。亦史记燕世家之文也。捏合而成之。然召公不说之说。自史记已谬误。且篇中何尝有不说之意欤。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周公称王命而命蔡仲也。只称王命。恐失事实。
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 史记伐淮夷在迁殷遗民之后。即三监同叛之时也。孔安国云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者何也。然则周公诛武庚而置奄不之诛乎。郑玄亦曰此即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
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蒲。马本作薄。) 孔安国云告召公使作册书告令之。正义云篇亡不知告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为此策书告令。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此序在宗周以上。用史记。而此篇首叙王来自奄。而多士书曰昔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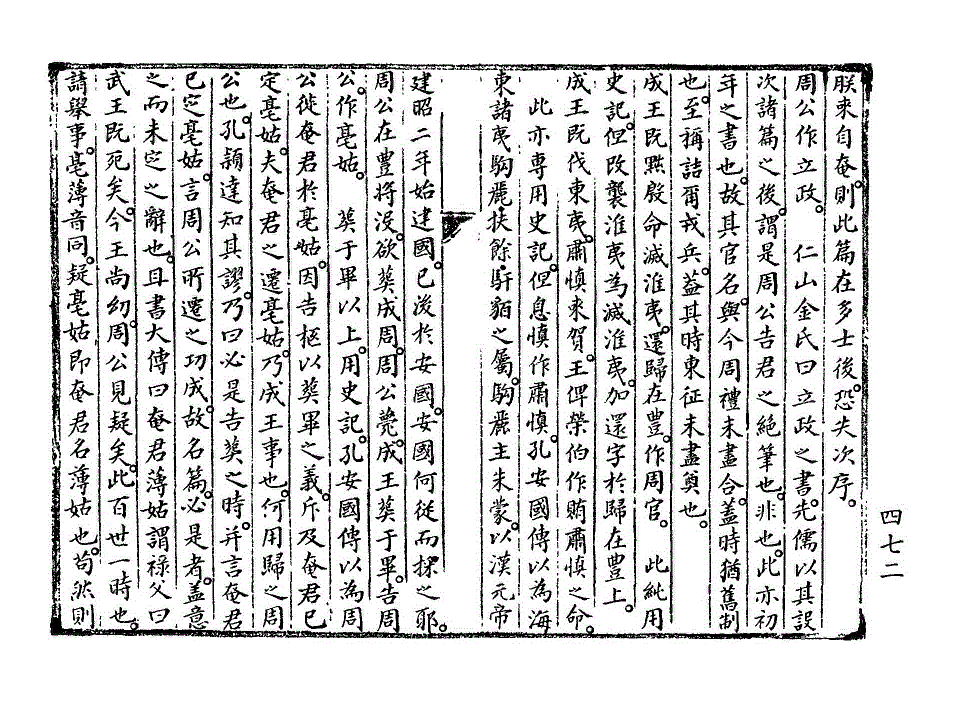 朕来自奄。则此篇在多士后。恐失次序。
朕来自奄。则此篇在多士后。恐失次序。周公作立政。 仁山金氏曰立政之书。先儒以其设次诸篇之后。谓是周公告君之绝笔也。非也。此亦初年之书也。故其官名。与今周礼未尽合。盖时犹旧制也。至称诘尔戎兵。盖其时东征未尽奠也。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礼。作周官。 此纯用史记。但改袭淮夷为灭淮夷。加还字于归在礼上。
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此亦专用史记。但息慎作肃慎。孔安国传以为海东诸夷驹丽,扶馀,馯貊之属。驹丽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已后于安国。安国何从而采之耶。
周公在礼将没。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 葬于毕以上。用史记。孔安国传以为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毕之义。斥及奄君已定亳姑。夫奄君之迁亳姑。乃成王事也。何用归之周公也。孔颖达知其谬。乃曰必是告葬之时。并言奄君已定亳姑。言周公所迁之功成。故名篇。必是者。盖意之而未定之辞也。且书大传曰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一时也。请举事。亳薄音同。疑亳姑即奄君名薄姑也。苟然则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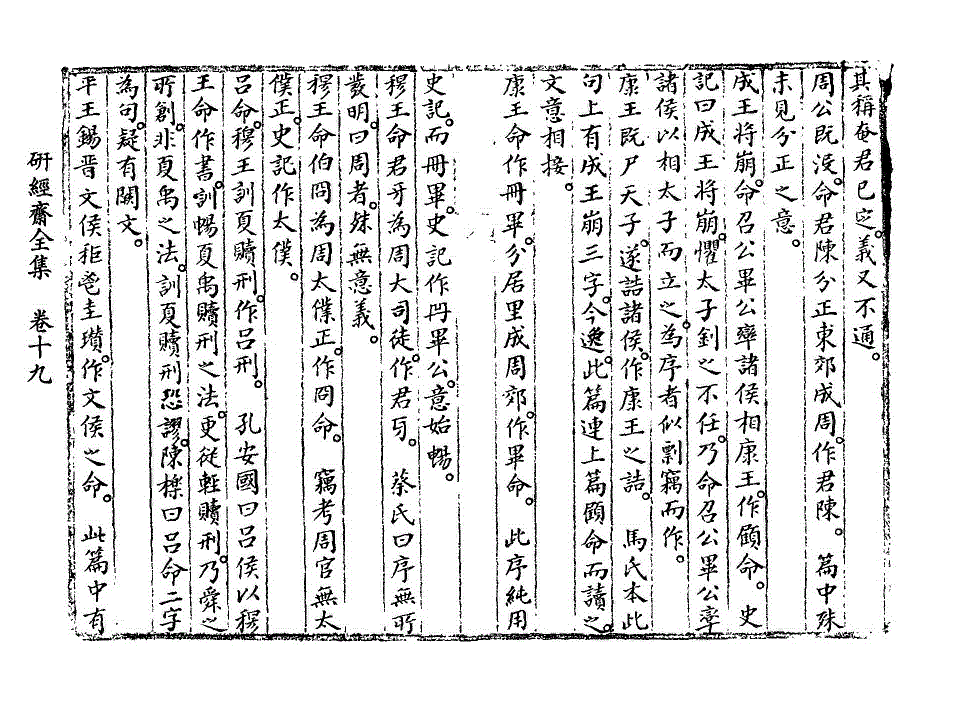 其称奄君已定。义又不通。
其称奄君已定。义又不通。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篇中殊未见分正之意。
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史记曰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为序者似剽窃而作。
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马氏本此句上有成王崩三字。今逸。此篇连上篇顾命而读之。文意相接。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此序纯用史记。而册毕。史记作册毕公。意始畅。
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蔡氏曰序无所发明。曰周者。殊无意义。
穆王命伯囧为周太仆正。作囧命。 窃考周官无太仆正。史记作太仆。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孔安国曰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赎刑。乃舜之所创。非夏禹之法。训夏赎刑恐谬。陈栎曰吕命二字为句。疑有阙文。
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此篇中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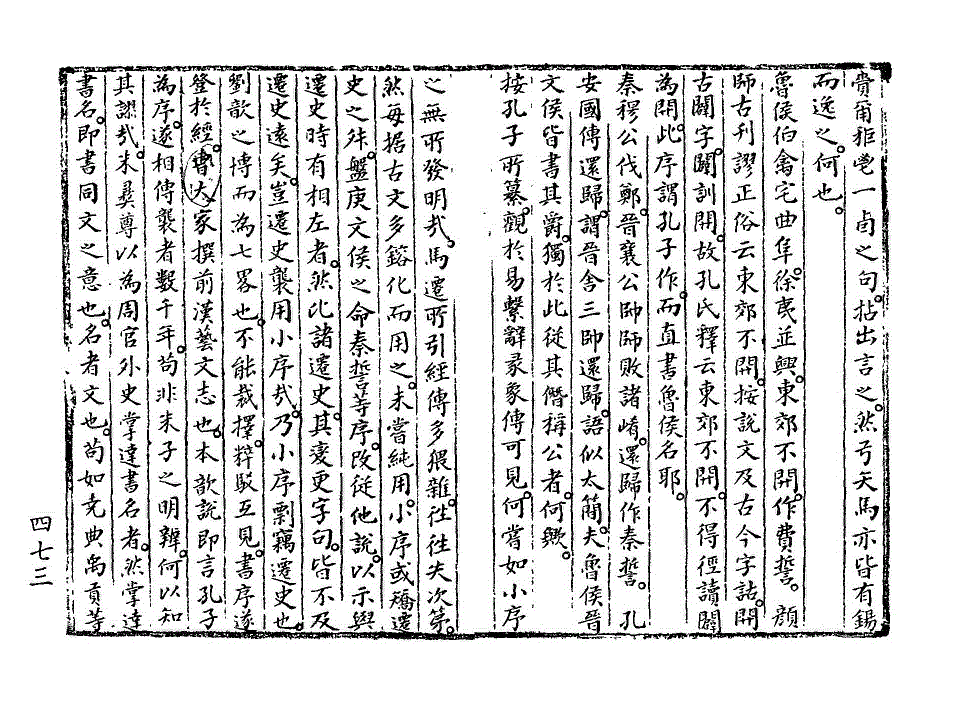 赍尔秬鬯一卣之句。拈出言之。然弓矢马亦皆有锡而逸之。何也。
赍尔秬鬯一卣之句。拈出言之。然弓矢马亦皆有锡而逸之。何也。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孔安国传还归。谓晋舍三帅还归。语似太简。夫鲁侯晋文侯皆书其爵。独于此从其僭称公者。何欤。
按孔子所纂。观于易系辞彖象传可见。何尝如小序之无所发明哉。马迁所引经传多猥杂。往往失次第。然每据古文多镕化而用之。未尝纯用。小序或矫迁史之舛。盘庚文侯之命秦誓等序。改从他说。以示与迁史时有相左者。然比诸迁史。其变更字句。皆不及迁史远矣。岂迁史袭用小序哉。乃小序剽窃迁史也。刘歆之博而为七略也。不能裁择。粹驳互见。书序遂登于经。曹大家撰前汉艺文志也。本歆说即言孔子为序。遂相传袭者数千年。苟非朱子之明辨。何以知其谬哉。朱彝尊以为周官外史掌达书名者。然掌达书名。即书同文之意也。名者文也。苟如尧典禹贡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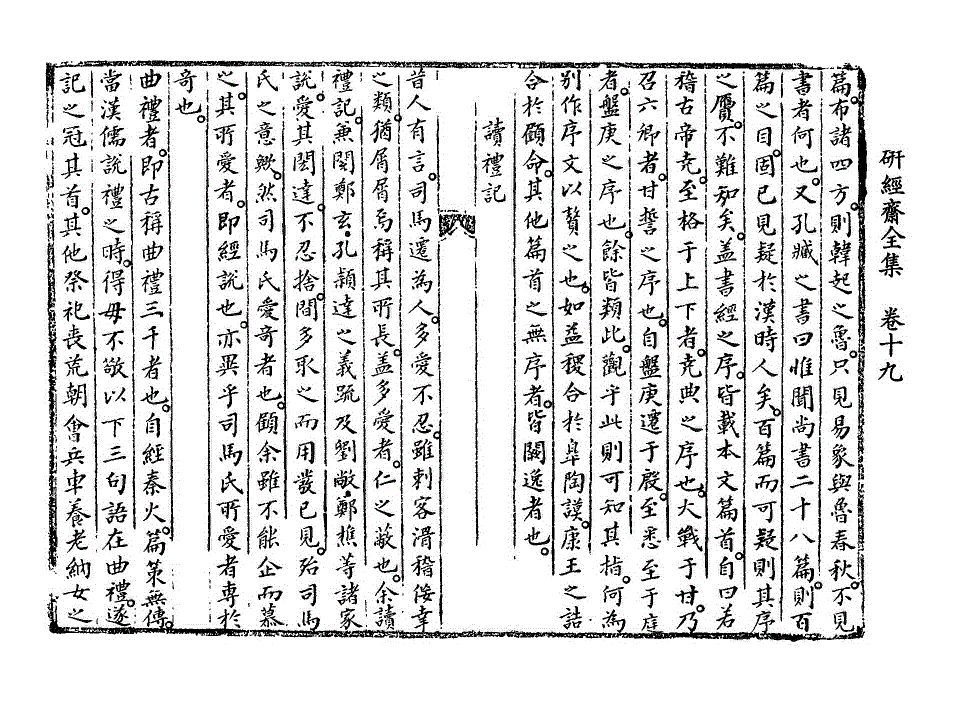 篇。布诸四方。则韩起之鲁。只见易象与鲁春秋。不见书者何也。又孔臧之书曰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则百篇之目。固已见疑于汉时人矣。百篇而可疑则其序之赝。不难知矣。盖书经之序。皆载本文篇首。自曰若稽古帝尧。至格于上下者。尧典之序也。大战于甘。乃召六卿者。甘誓之序也。自盘庚迁于殷。至悉至于庭者。盘庚之序也。馀皆类此。观乎此则可知其指。何为别作序文以赘之也。如益稷合于皋陶谟。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其他篇首之无序者。皆阙逸者也。
篇。布诸四方。则韩起之鲁。只见易象与鲁春秋。不见书者何也。又孔臧之书曰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则百篇之目。固已见疑于汉时人矣。百篇而可疑则其序之赝。不难知矣。盖书经之序。皆载本文篇首。自曰若稽古帝尧。至格于上下者。尧典之序也。大战于甘。乃召六卿者。甘誓之序也。自盘庚迁于殷。至悉至于庭者。盘庚之序也。馀皆类此。观乎此则可知其指。何为别作序文以赘之也。如益稷合于皋陶谟。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其他篇首之无序者。皆阙逸者也。读礼记
昔人有言。司马迁为人。多爱不忍。虽刺客滑稽佞幸之类。犹屑屑焉称其所长。盖多爱者。仁之蔽也。余读礼记。兼阅郑玄,孔颖达之义疏及刘敞,郑樵等诸家说。爱其闳达。不忍舍。间多取之而用发己见。殆司马氏之意欤。然司马氏爱奇者也。顾余虽不能企而慕之。其所爱者。即经说也。亦异乎司马氏所爱者专于奇也。
曲礼者。即古称曲礼三千者也。自经秦火。篇策无传。当汉儒说礼之时。得毋不敬以下三句语在曲礼。遂记之冠其首。其他祭祀丧荒朝会兵车养老纳女之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4L 页
 事。皆仪也。非礼也。零碎委琐。不相伦理。如抟饭齧骨投狗等细节。苟少涉于礼者。自可无此。不必书戒。然则此篇为礼记篇首者何也。五礼之仪。举其槩略。皆具于此。非如乐记祭义等偏于一者。又其所记。自日用常行始。故为之首。顾其文甚奇。可讽其意而习其节耳。或以为偏曲一端。或以为细微曲折皆通。
事。皆仪也。非礼也。零碎委琐。不相伦理。如抟饭齧骨投狗等细节。苟少涉于礼者。自可无此。不必书戒。然则此篇为礼记篇首者何也。五礼之仪。举其槩略。皆具于此。非如乐记祭义等偏于一者。又其所记。自日用常行始。故为之首。顾其文甚奇。可讽其意而习其节耳。或以为偏曲一端。或以为细微曲折皆通。檀弓所论。皆丧礼也。错以流俗妄语。盖粹驳互见之书也。举其可疑者数条。孔子负杖逍遥而曰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夫两楹之间。南面之位也。曾子,子张学不及圣人。犹临没而致慎焉。圣人岂复慨时俗之不尊已。眷眷于正终之际乎。其与凤鸟不至之叹殊矣。又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然出母绝而未嫁者。父在则当服齐衰期。子上之母死而子思在焉。子上当服齐衰期。顾已嫁故不为之服。若不服嫁母而并不服出母。则岂子不绝母之义乎。此恐记者过也。孔颖达云名檀弓者。以其善于礼。故著姓名显之。然篇中不复见其论礼。则未必因其善礼而著之。特因篇首偶有所著。故因以著之耳。
王制。卢植曰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孔颖达曰王制之作。在秦汉之际。今考其说。其论封建受田授地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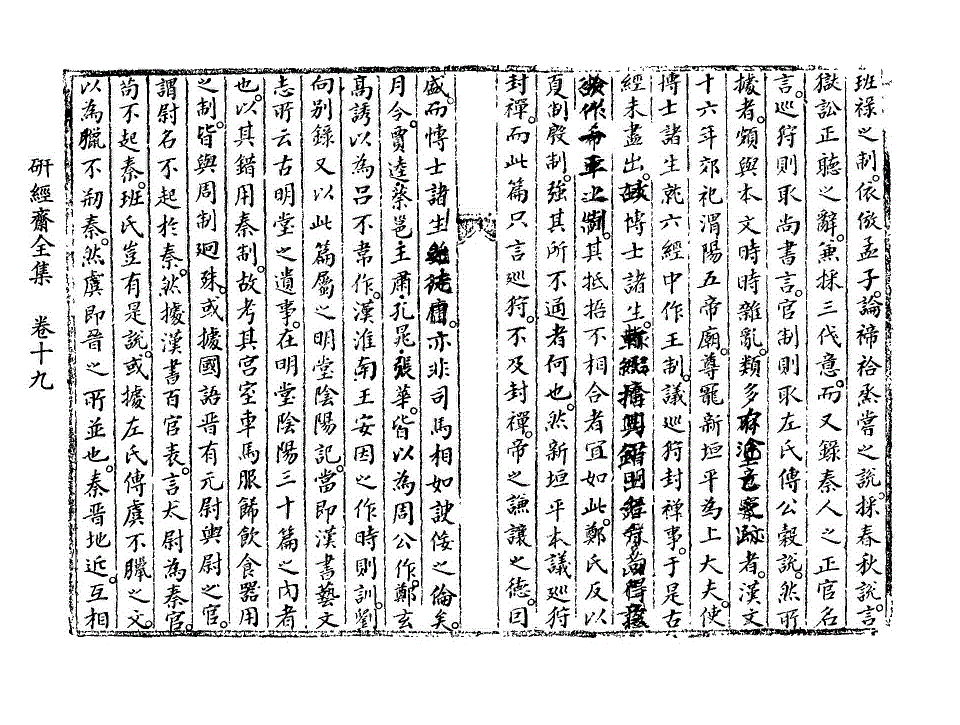 班禄之制。依仿孟子。论禘祫烝尝之说。采春秋说。言狱讼正听之辞。兼采三代意。而又录秦人之正官名言。巡狩则取尚书言。官制则取左氏传公谷说。然所据者。颇与本文时时杂乱。类多有涂乙之迹者。汉文十六年郊祀渭阳五帝庙。尊宠新垣平为上大夫。使博士诸生就六经中作王制。议巡狩封禅事。于是古经未尽出。故博士诸生。辄缀拾其错出者。参以己意。欲作一王之制。其牴牾不相合者宜如此。郑氏反以夏制殷制。强其所不通者何也。然新垣平本议巡狩封禅。而此篇只言巡狩。不及封禅。帝之谦让之德。因盛。而博士诸生之徒。亦非司马相如谀佞之伦矣。
班禄之制。依仿孟子。论禘祫烝尝之说。采春秋说。言狱讼正听之辞。兼采三代意。而又录秦人之正官名言。巡狩则取尚书言。官制则取左氏传公谷说。然所据者。颇与本文时时杂乱。类多有涂乙之迹者。汉文十六年郊祀渭阳五帝庙。尊宠新垣平为上大夫。使博士诸生就六经中作王制。议巡狩封禅事。于是古经未尽出。故博士诸生。辄缀拾其错出者。参以己意。欲作一王之制。其牴牾不相合者宜如此。郑氏反以夏制殷制。强其所不通者何也。然新垣平本议巡狩封禅。而此篇只言巡狩。不及封禅。帝之谦让之德。因盛。而博士诸生之徒。亦非司马相如谀佞之伦矣。月令。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玄高诱以为吕不韦作。汉淮南王安因之作时则训。刘向别录又以此篇属之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篇之内者也。以其错用秦制。故考其宫室车马服饰饮食器用之制。皆与周制迥殊。或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官。谓尉名不起于秦。然据汉书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苟不起秦。班氏岂有是说。或据左氏传虞不腊之文。以为腊不刱秦。然虞即晋之所并也。秦晋地近。互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5L 页
 习用。亦其理也。或以为不韦死后十六年并天下。以十月为岁首。非不韦所刱。然秦代周火德为水德。而不韦当庄襄时灭东周。已著定时历。至始皇二十六年。始灭六国。而行之无疑也。盖不韦多宾客。故好聚战国诸书。如邹衍所著主运等篇。牵缀之而成。然帝王发号施令之大端。颇章章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行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灾异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
习用。亦其理也。或以为不韦死后十六年并天下。以十月为岁首。非不韦所刱。然秦代周火德为水德。而不韦当庄襄时灭东周。已著定时历。至始皇二十六年。始灭六国。而行之无疑也。盖不韦多宾客。故好聚战国诸书。如邹衍所著主运等篇。牵缀之而成。然帝王发号施令之大端。颇章章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行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灾异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曾子问所记。皆丧变礼祭变礼。曾子之学。以鲁得之。所问皆切实。而孔子之答也。往往有未喻者。即已觉其义。更无发难于其间如子贡子夏之问诗礼者。岂亦未闻一贯之前欤。篇中所引老聃之言颇多。此孔子问礼老聃之證也。顾郑注释老聃曰古寿考者之号也。后人或疑非老子。然其称引者如史佚鲁侯伯禽者。皆周故事也。老子为周柱下史故识之。不当疑其非老子也。
文王世子篇简多错。然其旨义贯通。始于三代教胄之法。以及文武成三王之事。盖因世子之记而起。但未知世子之记。起自何世也。夫教莫先于礼。礼莫先于养老尊贤。故其序秩如也。且及庶子者。亲亲之谊也。以世子故。序庶子本支百世者。义在斯乎。但周公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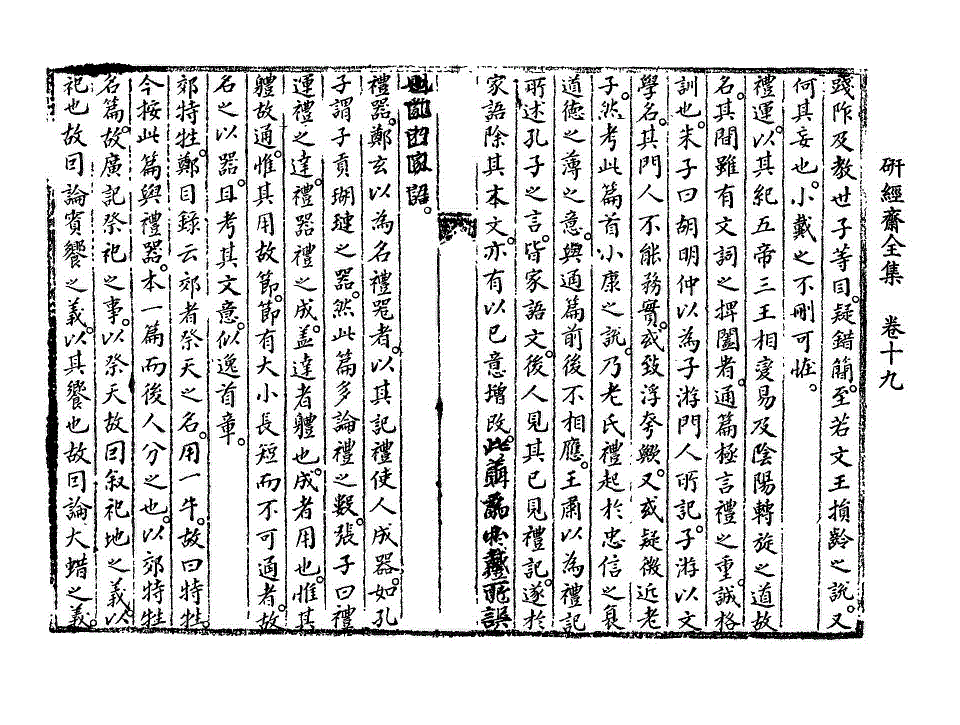 践阼及教世子等目。疑错简。至若文王损龄之说。又何其妄也。小戴之不删可怪。
践阼及教世子等目。疑错简。至若文王损龄之说。又何其妄也。小戴之不删可怪。礼运。以其纪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转旋之道故名。其间虽有文词之捭阖者。通篇极言礼之重。诚格训也。朱子曰胡明仲以为子游门人所记。子游以文学名。其门人不能务实。或致浮夸欤。又或疑微近老子。然考此篇首小康之说。乃老氏礼起于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与通篇前后不相应。王肃以为礼记所述孔子之言。皆家语文。后人见其已见礼记。遂于家语除其本文。亦有以己意增改。此则为小戴所误也。
礼器。郑玄以为名礼器者。以其记礼使人成器。如孔子谓子贡瑚琏之器。然此篇多论礼之数。张子曰礼运礼之达。礼器礼之成。盖达者体也。成者用也。惟其体故通。惟其用故节。节有大小长短而不可通者。故名之以器。且考其文意。似逸首章。
郊特牲。郑目录云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今按此篇与礼器。本一篇而后人分之也。以郊特牲名篇。故广记祭祀之事。以祭天故因叙祀地之义。以祀也故因论宾飨之义。以其飨也故因论大蜡之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6L 页
 然而特眷眷于堂陛之分。深斥诸侯大夫之僭礼。而屡及三桓。殆孔子之遗意也。若其自冠义以下一段。当属冠义而逸者也。自天地合以下一段。当属昏义而逸者也。
然而特眷眷于堂陛之分。深斥诸侯大夫之僭礼。而屡及三桓。殆孔子之遗意也。若其自冠义以下一段。当属冠义而逸者也。自天地合以下一段。当属昏义而逸者也。内则。郑玄云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故名。其记饮食调治之法为详。甚宜于养老。不知所记者何人。然观其牛夜鸣等句。取于周礼五十养于乡一章杂于王制。盖牵缀零琐而成者也。最与曲礼相出入。又因饮食之事。以及天子之养老。又因居室之事。以及国君世子生之法。盖通上下之辞。是故记者因说后王命冢宰之训而起之。
玉藻。郑玄以为记服冕之事。冕旒以藻紃贯玉为饰故名。然较诸篇脱乱为甚。方说朝服之制。忽又说飨食之法。方说车服之制。忽又说盥沐之事。方说献上之礼。忽又说事亲之仪。方说容色之仪。忽又说称谓之辞。错杂混淆。殊与郑意异矣。中庸大学章句。为先儒所定而后可读。玉藻而独不然乎。
明堂位别录。属明堂阴阳。郑玄以为诸侯朝周公于明堂。所陈列之位。然观其文义。周公以诸侯朝也。不然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者。属之谁人也。夫周公摄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7H 页
 位之说。始于荀卿。盖当成王谅闇时。周公在冢宰之位。代行天子之政。如百官揔己。以听冢宰者也。鲁人誇鲁之盛。遂及周公之功之德。得用天子之礼乐。如閟宫诗之浮夸。即其验也。流俗之见闻。传为美事。窃意汉武时徵鲁诸生议明堂事。此篇遂得彰明于世。然所以夸大者。适足以著其僭也。至如君臣未尝相弑。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之言。春秋左氏所传。可独诬乎。
位之说。始于荀卿。盖当成王谅闇时。周公在冢宰之位。代行天子之政。如百官揔己。以听冢宰者也。鲁人誇鲁之盛。遂及周公之功之德。得用天子之礼乐。如閟宫诗之浮夸。即其验也。流俗之见闻。传为美事。窃意汉武时徵鲁诸生议明堂事。此篇遂得彰明于世。然所以夸大者。适足以著其僭也。至如君臣未尝相弑。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之言。春秋左氏所传。可独诬乎。丧服小记。郑玄以为记丧服之小义故名。朱子曰小记是解丧服传。丧服传既有记。而此记又其纤琐者。盖丧服有传而释之。有记而续之。又有小记而继之。古人之致意于丧服如此。岂亦子夏门人所记欤。篇中有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然庶子之子为士立祢庙。则可得祭父之生母也。
大传。与仪礼丧服传互出。但丧服传逐章而释之。此篇即泛论之。如易大传尚书大传之类。窃意前志有全文。而作者互相引之。或入丧服传。或入此篇。然此篇剖析论列。比丧服传益明矣。其论昏姻之事。引周制甚正。春秋左氏传叔詹之言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产之言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此皆言生产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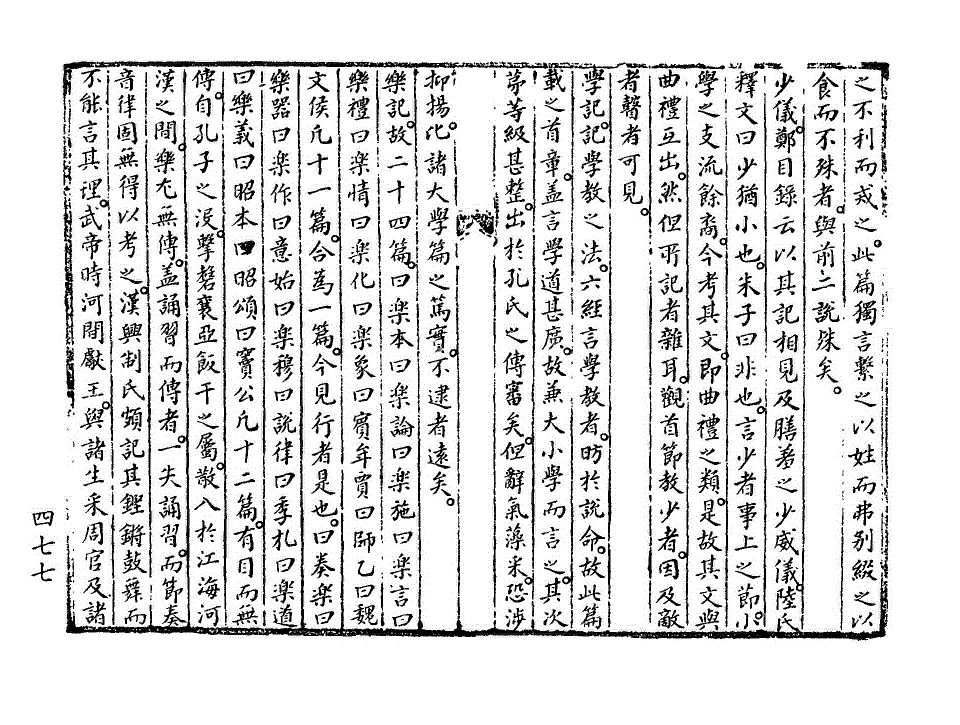 之不利而戒之。此篇独言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不殊者。与前二说殊矣。
之不利而戒之。此篇独言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不殊者。与前二说殊矣。少仪。郑目录云以其记相见及膳羞之少威仪。陆氏释文曰少犹小也。朱子曰非也。言少者事上之节。小学之支流馀裔。今考其文。即曲礼之类。是故其文与曲礼互出。然但所记者杂耳。观首节教少者。因及敌者𥌒者可见。
学记。记学教之法。六经言学教者。昉于说命。故此篇载之首章。盖言学道甚广。故兼大小学而言之。其次第等级甚整。出于孔氏之传审矣。但辞气藻采。恐涉抑扬。比诸大学篇之笃实。不逮者远矣。
乐记。故二十四篇。曰乐本曰乐论曰乐施曰乐言曰乐礼曰乐情曰乐化曰乐象曰宾牟贾曰师乙曰魏文侯凡十一篇。合为一篇。今见行者是也。曰奏乐曰乐器曰乐作曰意始曰乐穆曰说律曰季札曰乐道曰乐义曰昭本曰昭颂曰窦公凡十二篇。有目而无传。自孔子之没。击磬襄亚饭干之属。散入于江海河汉之间。乐尤无传。盖诵习而传者。一失诵习。而节奏音律固无得以考之。汉兴制氏颇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理。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采周官及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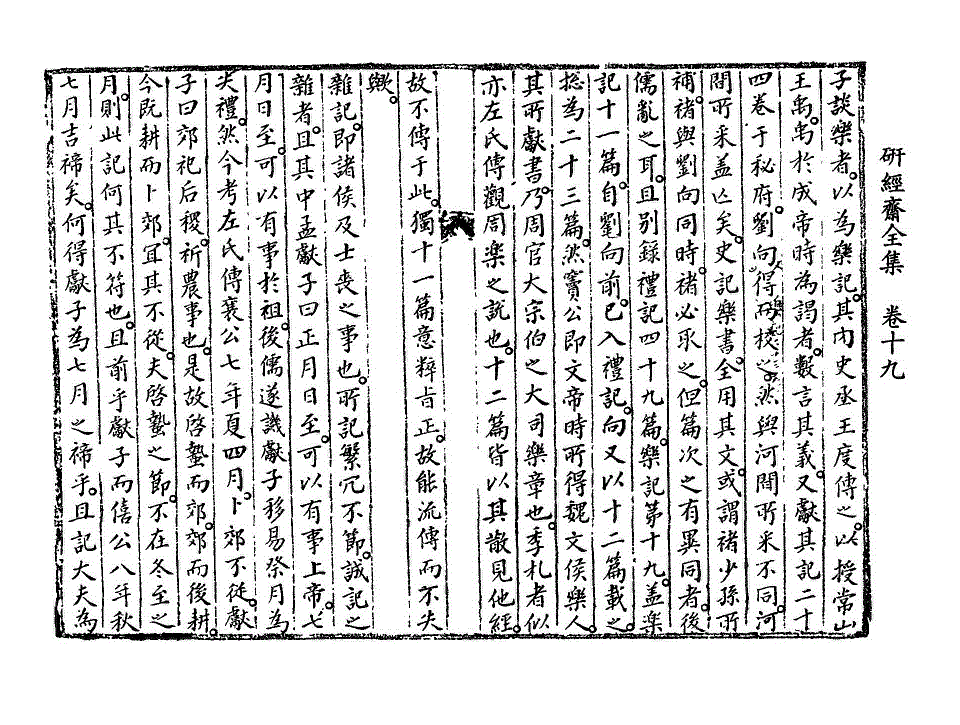 子谈乐者。以为乐记。其内史丞王度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于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又献其记二十四卷于秘府。刘向又得乐记二十二卷而校之。然与河间所采不同。河间所采盖亡矣。史记乐书。全用其文。或谓褚少孙所补。褚与刘向同时。褚必取之。但篇次之有异同者。后儒乱之耳。且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盖乐记十一篇。自刘向前。已入礼记。向又以十二篇载之。总为二十三篇。然窦公即文帝时所得魏文侯乐人。其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季札者似亦左氏传观周乐之说也。十二篇皆以其散见他经。故不传于此。独十一篇意粹旨正。故能流传而不失欤。
子谈乐者。以为乐记。其内史丞王度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于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又献其记二十四卷于秘府。刘向又得乐记二十二卷而校之。然与河间所采不同。河间所采盖亡矣。史记乐书。全用其文。或谓褚少孙所补。褚与刘向同时。褚必取之。但篇次之有异同者。后儒乱之耳。且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盖乐记十一篇。自刘向前。已入礼记。向又以十二篇载之。总为二十三篇。然窦公即文帝时所得魏文侯乐人。其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季札者似亦左氏传观周乐之说也。十二篇皆以其散见他经。故不传于此。独十一篇意粹旨正。故能流传而不失欤。杂记。即诸侯及士丧之事也。所记繁冗不节。诚记之杂者。且其中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后儒遂讥献子移易祭月为失礼。然今考左氏传襄公七年夏四月。卜郊不从。献子曰郊祀后稷。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夫启蛰之节。不在冬至之月。则此记何其不符也。且前乎献子而僖公八年秋七月吉禘矣。何得献子为七月之禘乎。且记大夫为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8L 页
 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丧服如士服者。郑氏以为大夫丧礼。与士异。然父母之丧。自天子达。又安有大夫士之殊乎。意因晏子惟卿为大夫之语而转致此也。
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丧服如士服者。郑氏以为大夫丧礼。与士异。然父母之丧。自天子达。又安有大夫士之殊乎。意因晏子惟卿为大夫之语而转致此也。丧大记。记人君以下始死小敛大敛殡祭之大事。郑玄目录刘元云记谓之大者。以其委曲详备繁大故云。仪礼只有士丧礼。而无人君之礼。赖此篇所论可以徵也。若吉祭复寝之训。恐当以郑注为得。上既称禫。而从御岂复别生一义于吉祭后乎。盖指不宿中门外。复于殡宫之寝也。观孟献子比御而不入。夫子许以加于人一等者。知禫而从御之义矣。
祭法。通记人鬼天神地示之祭。沈清臣以为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偏于群神之义疏也。朱子又云一篇即国语柳下惠说。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后。如祀稷祀契之类。只是祭祖宗。此皆后人附会而成。故不免迁就。其言天子七庙一坛一墠之说。从金縢三坛同墠之文。古无是也。刘歆寝庙议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有三宗。周公举之以劝成王。由是言之。宗无数也。顾此祭法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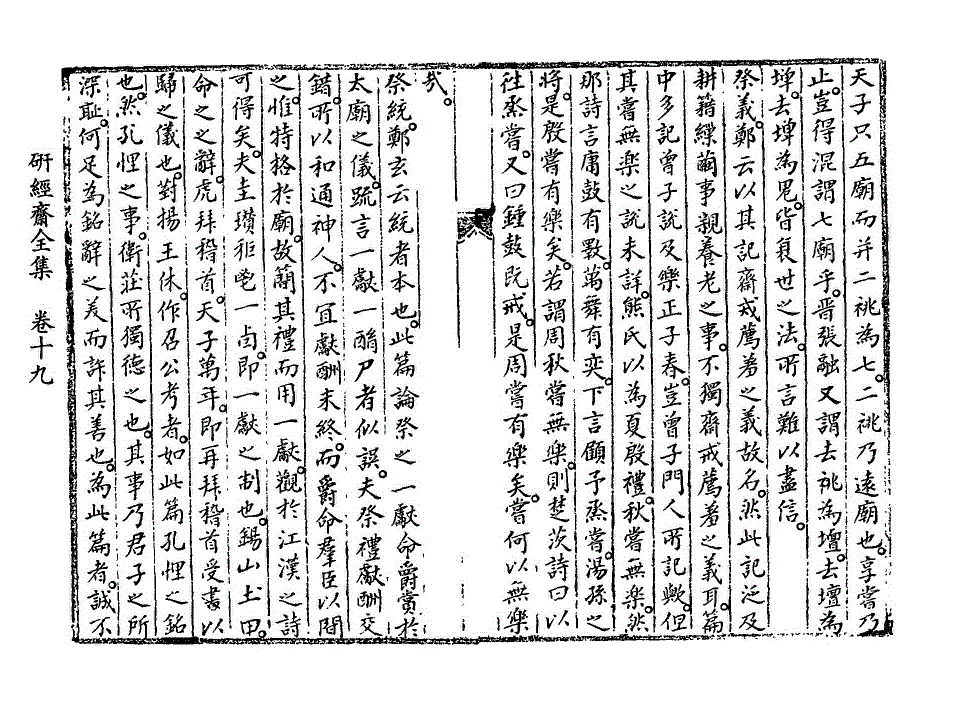 天子只五庙而并二祧为七。二祧乃远庙也。享尝乃止。岂得混谓七庙乎。晋张融又谓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皆衰世之法。所言难以尽信。
天子只五庙而并二祧为七。二祧乃远庙也。享尝乃止。岂得混谓七庙乎。晋张融又谓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皆衰世之法。所言难以尽信。祭义。郑云以其记斋戒荐羞之义故名。然此记泛及耕籍缫茧事亲养老之事。不独斋戒荐羞之义耳。篇中多记曾子说及乐正子春。岂曾子门人所记欤。但其尝无乐之说未详。熊氏以为夏殷礼。秋尝无乐。然那诗言庸鼓有斁。万舞有奕。下言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是殷尝有乐矣。若谓周秋尝无乐。则楚茨诗曰以往烝尝。又曰钟鼓既戒。是周尝有乐矣。尝何以无乐哉。
祭统。郑玄云统者本也。此篇论祭之一献命爵赏于太庙之仪。疏言一献一酳尸者似误。夫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酬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格于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观于江汉之诗可得矣。夫圭瓒秬鬯一卣。即一献之制也。锡山土田。命之之辞。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即再拜稽首受书以归之仪也。对扬王休。作召公考者。如此篇孔悝之铭也。然孔悝之事。卫庄所独德之也。其事乃君子之所深耻。何足为铭辞之美而许其善也。为此篇者。诚不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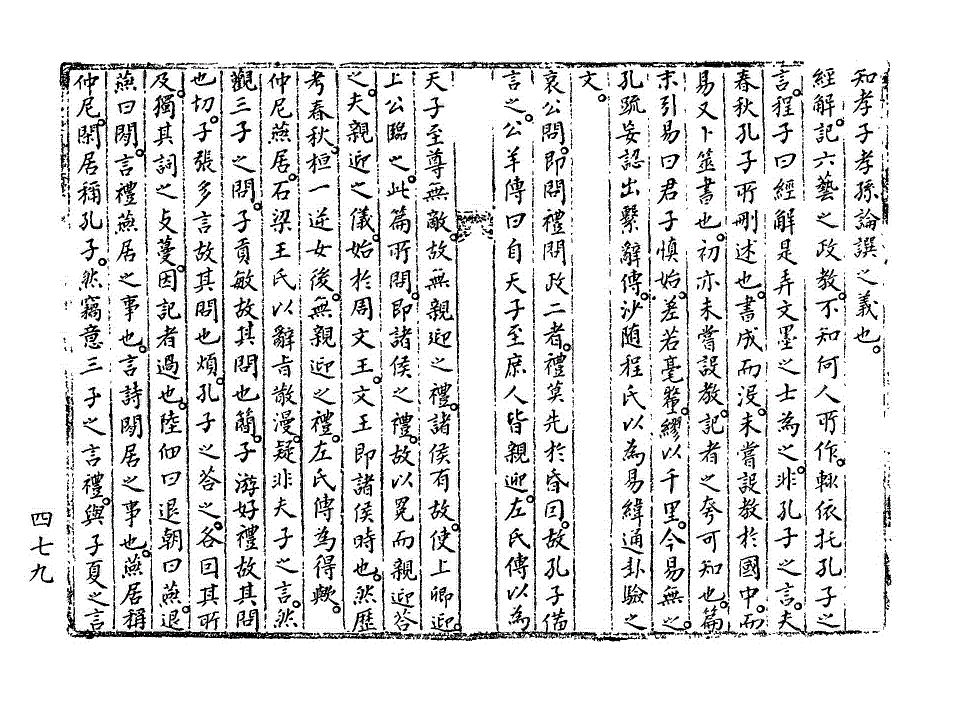 知孝子孝孙论撰之义也。
知孝子孝孙论撰之义也。经解。记六艺之政教。不知何人所作。辄依托孔子之言。程子曰经解是弄文墨之士为之。非孔子之言。夫春秋孔子所删述也。书成而没。未尝设教于国中。而易又卜筮书也。初亦未尝设教。记者之夸可知也。篇末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缪以千里。今易无之。孔疏妄认出系辞传。沙随程氏以为易纬通卦验之文。
哀公问。即问礼问政二者。礼莫先于昏因。故孔子备言之。公羊传曰自天子至庶人皆亲迎。左氏传以为天子至尊无敌。故无亲迎之礼。诸侯有故。使上卿迎。上公临之。此篇所问。即诸侯之礼。故以冕而亲迎答之。夫亲迎之仪。始于周文王。文王即诸侯时也。然历考春秋。桓一逆女后。无亲迎之礼。左氏传为得欤。
仲尼燕居。石梁王氏以辞旨散漫。疑非夫子之言。然观三子之问。子贡敏故其问也简。子游好礼故其问也切。子张多言故其问也烦。孔子之答之。各因其所及。独其词之支蔓。因记者过也。陆佃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礼燕居之事也。言诗閒居之事也。燕居称仲尼。闲居称孔子。然窃意三子之言礼。与子夏之言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0H 页
 诗不同时。记者或称仲尼。或称孔子。似非有意于其间也。
诗不同时。记者或称仲尼。或称孔子。似非有意于其间也。孔子閒居。记子夏问答之辞。子夏以文学名。故以诗发之。世称毛诗发自子夏者是也。
坊记。似出于七十子之门人所记。要非完书。每章称子云。或各述其师言。未必皆孔子言。至若鲁昭公吴孟子事。夫子所讳者也。此篇中备言其去姓之故。且称鲁春秋。春秋即夫子所定者也。其旨多微婉。岂容自解其例若是之明哉。殊异乎知我罪我之训矣。
表记。固多格言。然亦坊记之类也。表者测日之臬也。四方所取正也。坊记示人以所当戒。表记示人以所当法也。但篇中有云事君远而谏则谄也此一段。恐非孔子之言。孔子之言。散在左氏传。而记者多错。如泄冶之谏陈灵而死者。诚得矣。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又如赵盾之弑君。诚可诛也。而孔子曰越境乃免。疑春秋之际。多藉孔子之言而重之。实非孔子之言也。
缁衣。刘瓛以为公孙尼子所作。汉书艺文志称七十子之弟子。未知游何人之门也。杂引诗书易论语而间多窜乱。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语。取夫子之言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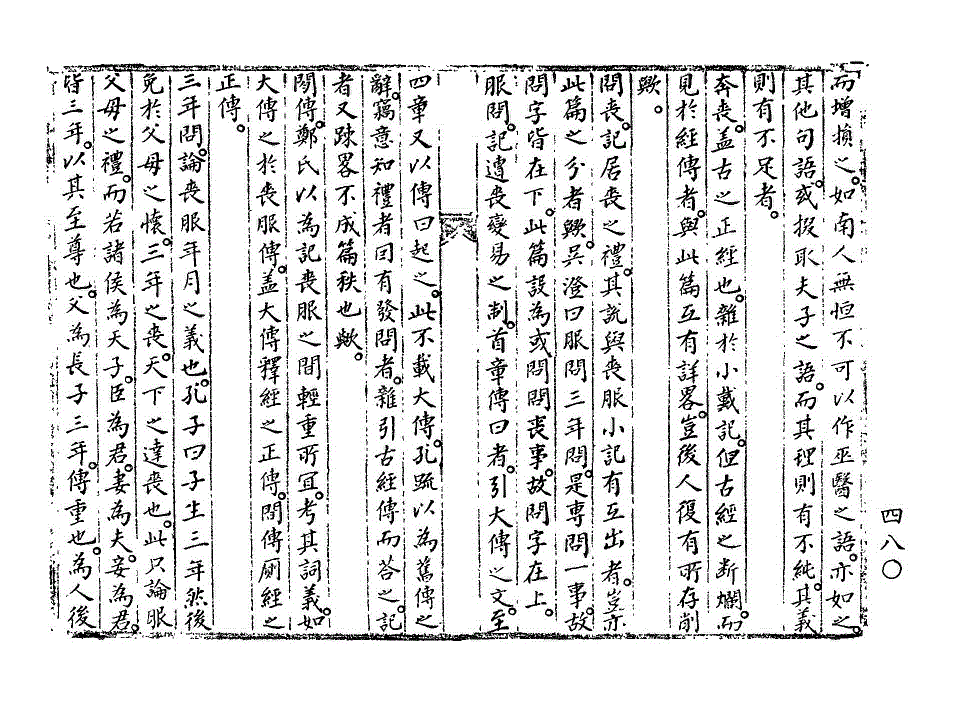 而增损之。如南人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之语。亦如之。其他句语。或掇取夫子之语。而其理则有不纯。其义则有不足者。
而增损之。如南人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之语。亦如之。其他句语。或掇取夫子之语。而其理则有不纯。其义则有不足者。奔丧。盖古之正经也。杂于小戴记。但古经之断烂。而见于经传者。与此篇互有详略。岂后人复有所存削欤。
问丧。记居丧之礼。其说与丧服小记有互出者。岂亦此篇之分者欤。吴澄曰服问三年问。是专问一事。故问字皆在下。此篇设为或问问丧事。故问字在上。
服问。记遭丧变易之制。首章传曰者。引大传之文。至四章又以传曰起之。此不载大传。孔疏以为旧传之辞。窃意知礼者因有发问者。杂引古经传而答之。记者又疏略不成篇秩也欤。
间传。郑氏以为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考其词义。如大传之于丧服传。盖大传释经之正传。间传厕经之正传。
三年问。论丧服年月之义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此只论服父母之礼。而若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妻为夫。妾为君。皆三年。以其至尊也。父为长子三年。传重也。为人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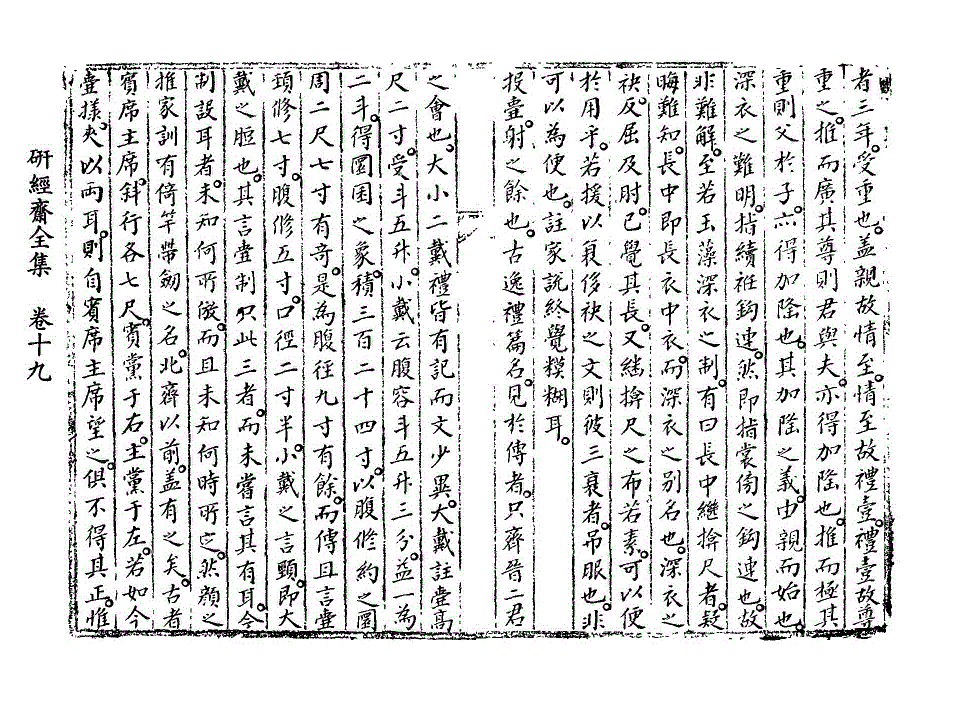 者三年。受重也。盖亲故情至。情至故礼壹。礼壹故尊重之。推而广其尊则君与夫。亦得加隆也。推而极其重则父于子。亦得加隆也。其加隆之义。由亲而始也。
者三年。受重也。盖亲故情至。情至故礼壹。礼壹故尊重之。推而广其尊则君与夫。亦得加隆也。推而极其重则父于子。亦得加隆也。其加隆之义。由亲而始也。深衣之难明。指续衽钩连。然即指裳傍之钩连也。故非难解。至若玉藻深衣之制。有曰长中继掩尺者。疑晦难知。长中即长衣中衣。而深衣之别名也。深衣之袂。反屈及肘。已觉其长。又继掩尺之布若素。可以便于用乎。若援以衰侈袂之文则彼三衰者。吊服也。非可以为便也。注家说终觉模糊耳。
投壶。射之馀也。古逸礼篇名。见于传者。只齐晋二君之会也。大小二戴礼皆有记而文少异。大戴注壶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云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为二斗。得圜囷之象。积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约之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为腹径九寸有馀。而传且言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小戴之言颈。即大戴之脰也。其言壶制只此三者。而未尝言其有耳。今制设耳者。未知何所仿。而且未知何时所定。然颜之推家训有倚竿带剑之名。北齐以前。盖有之矣。古者宾席主席。斜行各七尺。宾党于右。主党于左。若如今壶㨾。夹以两耳。则自宾席主席望之。俱不得其正。惟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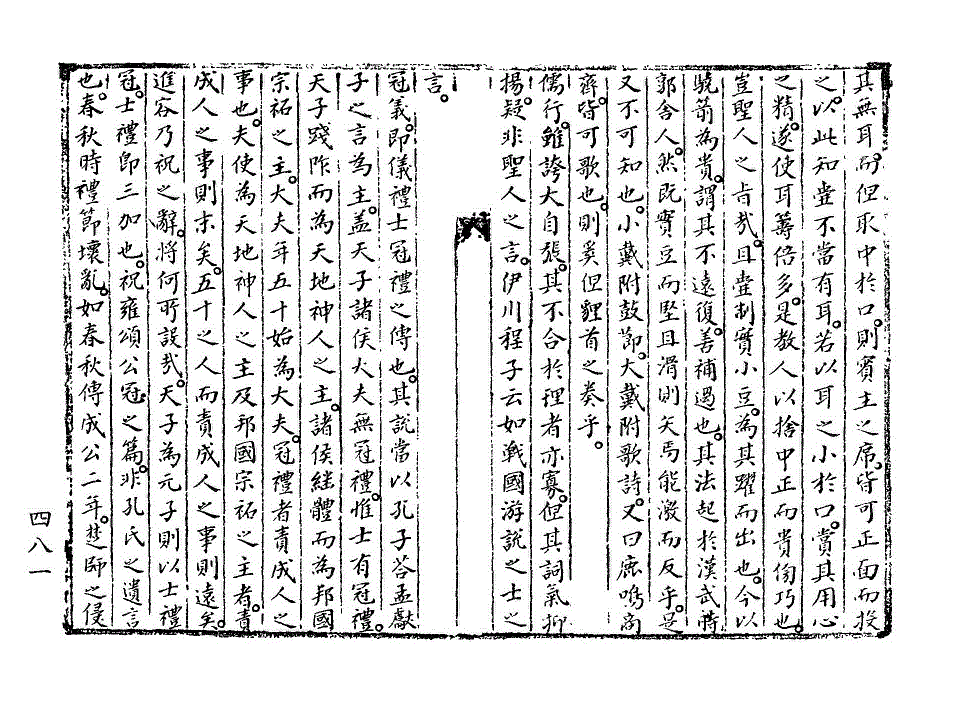 其无耳。而但取中于口。则宾主之席。皆可正面而投之。以此知壶不当有耳。若以耳之小于口。赏其用心之精。遂使耳筹倍多。是教人以舍中正而贵傍巧也。岂圣人之旨哉。且壶制实小豆。为其跃而出也。今以骁箭为贵。谓其不远复。善补过也。其法起于汉武时郭舍人。然既实豆而坚且滑则矢焉能激而反乎。是又不可知也。小戴附鼓节。大戴附歌诗。又曰鹿鸣商齐。皆可歌也。则奚但狸首之奏乎。
其无耳。而但取中于口。则宾主之席。皆可正面而投之。以此知壶不当有耳。若以耳之小于口。赏其用心之精。遂使耳筹倍多。是教人以舍中正而贵傍巧也。岂圣人之旨哉。且壶制实小豆。为其跃而出也。今以骁箭为贵。谓其不远复。善补过也。其法起于汉武时郭舍人。然既实豆而坚且滑则矢焉能激而反乎。是又不可知也。小戴附鼓节。大戴附歌诗。又曰鹿鸣商齐。皆可歌也。则奚但狸首之奏乎。儒行。虽誇大自张。其不合于理者亦寡。但其词气抑扬。疑非圣人之言。伊川程子云如战国游说之士之言。
冠义。即仪礼士冠礼之传也。其说当以孔子答孟献子之言为主。盖天子诸侯大夫无冠礼。惟士有冠礼。天子践阼而为天地神人之主。诸侯继体而为邦国宗祏之主。大夫年五十始为大夫。冠礼者责成人之事也。夫使为天地神人之主及邦国宗祏之主者。责成人之事则末矣。五十之人而责成人之事则远矣。进容乃祝之辞。将何所设哉。天子为元子则以士礼冠。士礼即三加也。祝雍颂公冠之篇。非孔氏之遗言也。春秋时礼节坏乱。如春秋传成公二年。楚师之侵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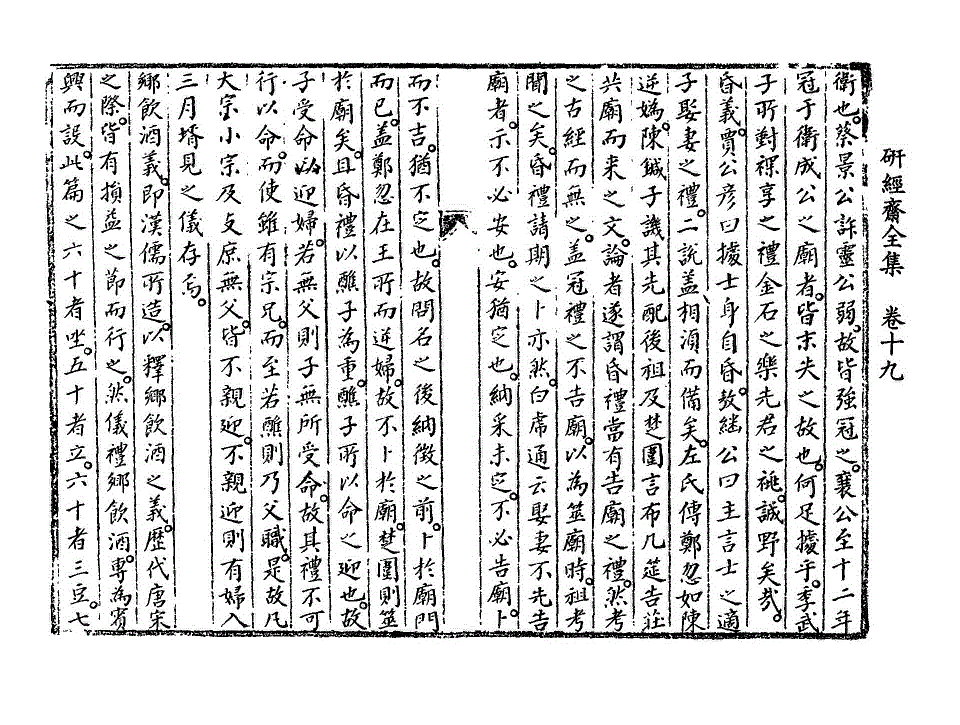 卫也。蔡景公许灵公弱。故皆强冠之。襄公至十二年冠于卫成公之庙者。皆末失之故也。何足据乎。季武子所对祼享之礼金石之乐先君之祧。诚野矣哉。
卫也。蔡景公许灵公弱。故皆强冠之。襄公至十二年冠于卫成公之庙者。皆末失之故也。何足据乎。季武子所对祼享之礼金石之乐先君之祧。诚野矣哉。昏义。贾公彦曰据士身自昏。敖继公曰主言士之适子娶妻之礼。二说盖相须而备矣。左氏传郑忽如陈逆妫。陈针子讥其先配后祖及楚围言布几筵告庄共庙而来之文。论者遂谓昏礼当有告庙之礼。然考之古经而无之。盖冠礼之不告庙。以为筮庙时。祖考闻之矣。昏礼请期之卜亦然。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庙者。示不必安也。安犹定也。纳采未定。不必告庙。卜而不吉。犹不定也。故问名之后纳徵之前。卜于庙门而已。盖郑忽在王所而逆妇。故不卜于庙。楚围则筮于庙矣。且昏礼以醮子为重。醮子所以命之迎也。故子受命以迎妇。若无父则子无所受命。故其礼不可行以命。而使虽有宗兄。而至若醮则乃父职。是故凡大宗,小宗及支庶无父。皆不亲迎。不亲迎则有妇入三月婿见之仪存焉。
乡饮酒义。即汉儒所造。以释乡饮酒之义。历代唐宋之际。皆有损益之节而行之。然仪礼乡饮酒。专为宾兴而设。此篇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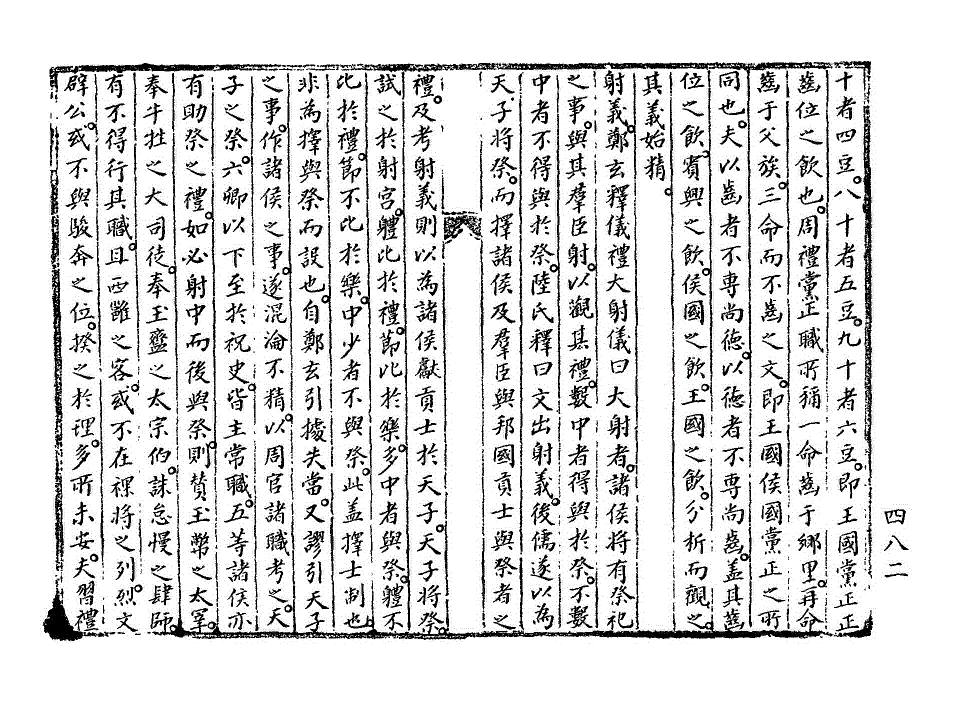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即王国党正正齿位之饮也。周礼党正职所称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之文。即王国侯国党正之所同也。夫以齿者不专尚德。以德者不专尚齿。盖其齿位之饮。宾兴之饮。侯国之饮。王国之饮。分析而观之。其义始精。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即王国党正正齿位之饮也。周礼党正职所称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之文。即王国侯国党正之所同也。夫以齿者不专尚德。以德者不专尚齿。盖其齿位之饮。宾兴之饮。侯国之饮。王国之饮。分析而观之。其义始精。射义。郑玄释仪礼大射仪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陆氏释曰文出射义。后儒遂以为天子将祭。而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贡士与祭者之礼。及考射义则以为诸侯献贡士于天子。天子将祭。试之于射宫。体比于礼。节比于乐。多中者与祭。体不比于礼。节不比于乐。中少者不与祭。此盖择士制也。非为择与祭而设也。自郑玄引据失当。又谬引天子之事。作诸侯之事。遂混沦不精。以周官诸职考之。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于祝史。皆主常职。五等诸侯亦有助祭之礼。如必射中而后与祭。则赞玉币之太宰。奉牛牲之大司徒。奉玉齍之太宗伯。诛怠慢之肆师。有不得行其职。且西雍之客。或不在祼将之列。烈文辟公。或不与骏奔之位。揆之于理。多所未安。夫习礼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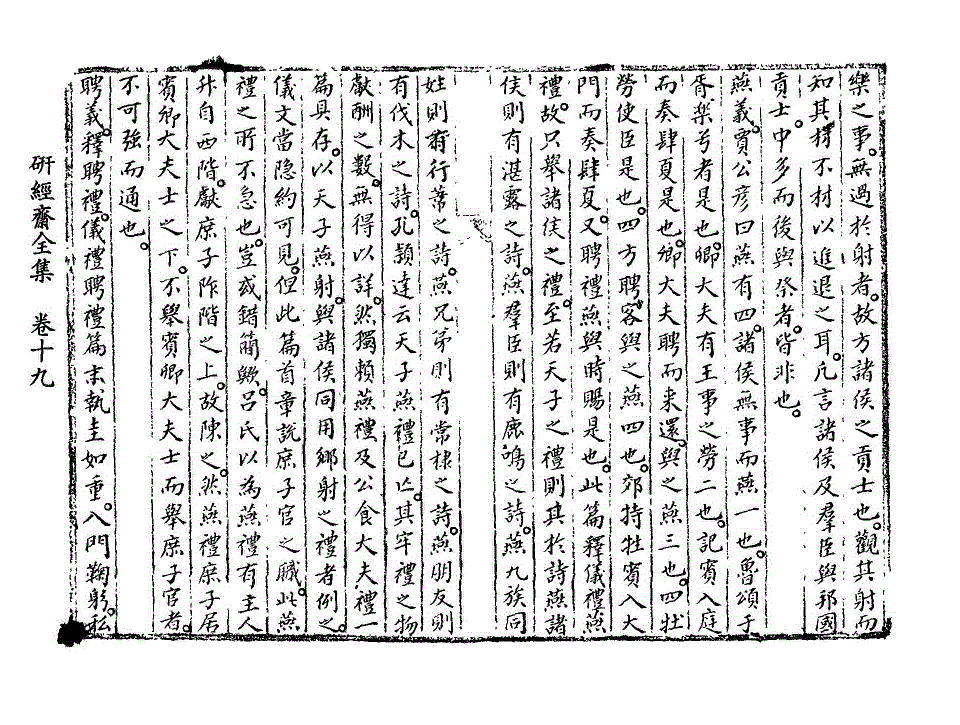 乐之事。无过于射者。故方诸侯之贡士也。观其射而知其材不材以进退之耳。凡言诸侯及群臣与邦国贡士。中多而后与祭者。皆非也。
乐之事。无过于射者。故方诸侯之贡士也。观其射而知其材不材以进退之耳。凡言诸侯及群臣与邦国贡士。中多而后与祭者。皆非也。燕义。贾公彦曰燕有四。诸侯无事而燕一也。鲁颂于胥乐兮者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记宾入庭而奏肆夏是也。卿大夫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牡劳使臣是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郊特牲宾入大门而奏肆夏。又聘礼燕与时赐是也。此篇释仪礼燕礼。故只举诸侯之礼。至若天子之礼则其于诗燕诸侯则有湛露之诗。燕群臣则有鹿鸣之诗。燕九族同姓则有行苇之诗。燕兄弟则有常棣之诗。燕朋友则有伐木之诗。孔颖达云天子燕礼已亡。其牢礼之物献酬之数。无得以详。然独赖燕礼及公食大夫礼一篇具存。以天子燕射。与诸侯同用乡射之礼者例之。仪文当隐约可见。但此篇首章说庶子官之职。此燕礼之所不急也。岂或错简欤。吕氏以为燕礼有主人升自西阶。献庶子阼阶之上。故陈之。然燕礼庶子居宾卿大夫士之下。不举宾卿大夫士而举庶子官者。不可强而通也。
聘义。释聘礼。仪礼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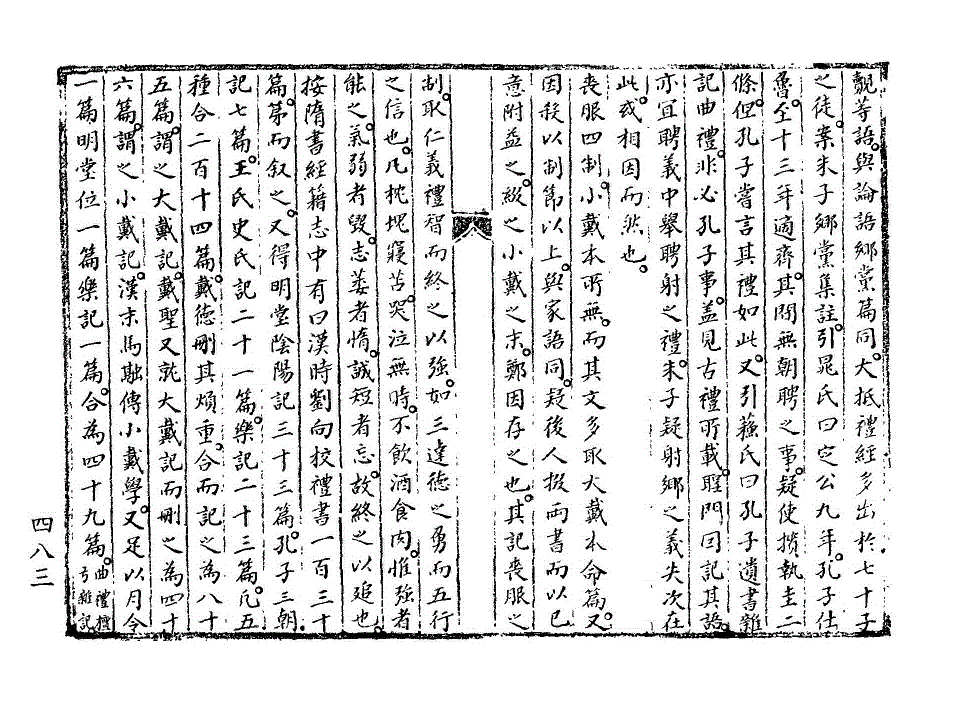 觌等语。与论语乡党篇同。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案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盖见古礼所载。圣门因记其语。亦宜聘义中举聘射之礼。朱子疑射乡之义失次在此。或相因而然也。
觌等语。与论语乡党篇同。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案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盖见古礼所载。圣门因记其语。亦宜聘义中举聘射之礼。朱子疑射乡之义失次在此。或相因而然也。丧服四制。小戴本所无。而其文多取大戴本命篇。又因杀以制节以上。与家语同。疑后人掇两书而以己意附益之。缀之小戴之末。郑因存之也。其记丧服之制。取仁义礼智而终之以强。如三达德之勇而五行之信也。凡枕块寝苫。哭泣无时。不饮酒食肉。惟强者能之。气弱者毁。志萎者惰。诚短者忘。故终之以追也。
按隋书经籍志中有曰汉时刘向校礼书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就大戴记而删之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传小戴学。又足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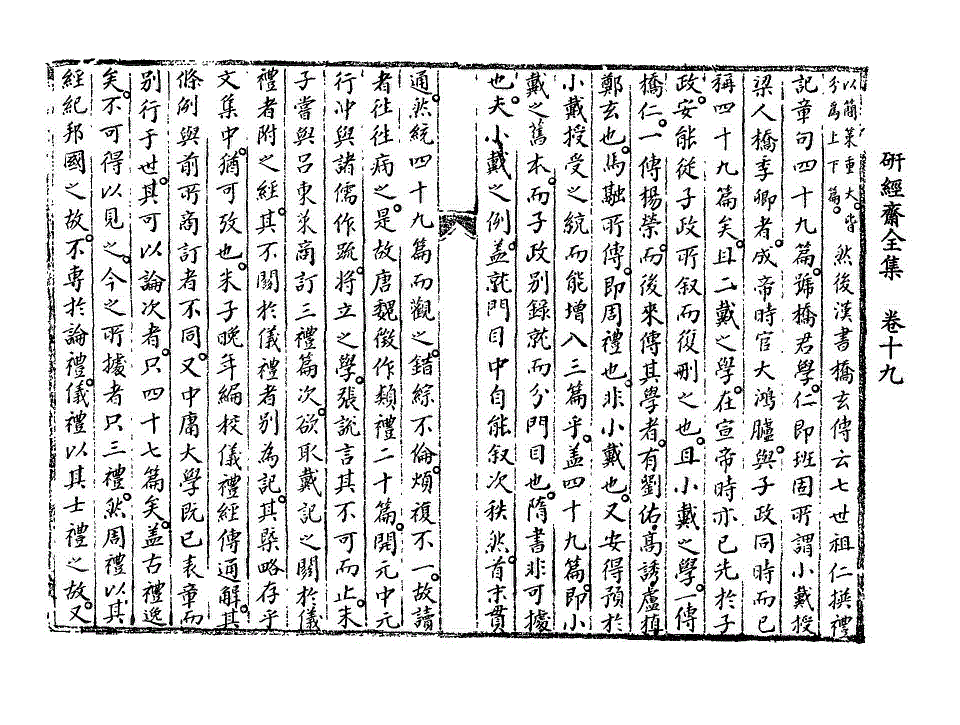 以简策重大。皆分为上下篇。)然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官大鸿胪。与子政同时而已称四十九篇矣。且二戴之学。在宣帝时亦已先于子政。安能从子政所叙而复删之也。且小戴之学。一传桥仁。一传杨荣。而后来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卢植,郑玄也。马融所传。即周礼也。非小戴也。又安得预于小戴授受之统而能增入三篇乎。盖四十九篇。即小戴之旧本。而子政别录就而分门目也。隋书非可据也。夫小戴之例。盖就门目中自能叙次秩然。首末贯通。然统四十九篇而观之。错综不伦。烦复不一。故读者往往病之。是故唐魏徵作类礼二十篇。开元中元行冲与诸儒作疏。将立之学。张说言其不可而止。朱子尝与吕东莱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之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关于仪礼者别为记。其槩略存乎文集中。犹可考也。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通解。其条例与前所商订者不同。又中庸大学既已表章而别行于世。其可以论次者。只四十七篇矣。盖古礼逸矣。不可得以见之。今之所据者只三礼。然周礼以其经纪邦国之故。不专于论礼。仪礼以其士礼之故。又
以简策重大。皆分为上下篇。)然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官大鸿胪。与子政同时而已称四十九篇矣。且二戴之学。在宣帝时亦已先于子政。安能从子政所叙而复删之也。且小戴之学。一传桥仁。一传杨荣。而后来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卢植,郑玄也。马融所传。即周礼也。非小戴也。又安得预于小戴授受之统而能增入三篇乎。盖四十九篇。即小戴之旧本。而子政别录就而分门目也。隋书非可据也。夫小戴之例。盖就门目中自能叙次秩然。首末贯通。然统四十九篇而观之。错综不伦。烦复不一。故读者往往病之。是故唐魏徵作类礼二十篇。开元中元行冲与诸儒作疏。将立之学。张说言其不可而止。朱子尝与吕东莱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之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关于仪礼者别为记。其槩略存乎文集中。犹可考也。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通解。其条例与前所商订者不同。又中庸大学既已表章而别行于世。其可以论次者。只四十七篇矣。盖古礼逸矣。不可得以见之。今之所据者只三礼。然周礼以其经纪邦国之故。不专于论礼。仪礼以其士礼之故。又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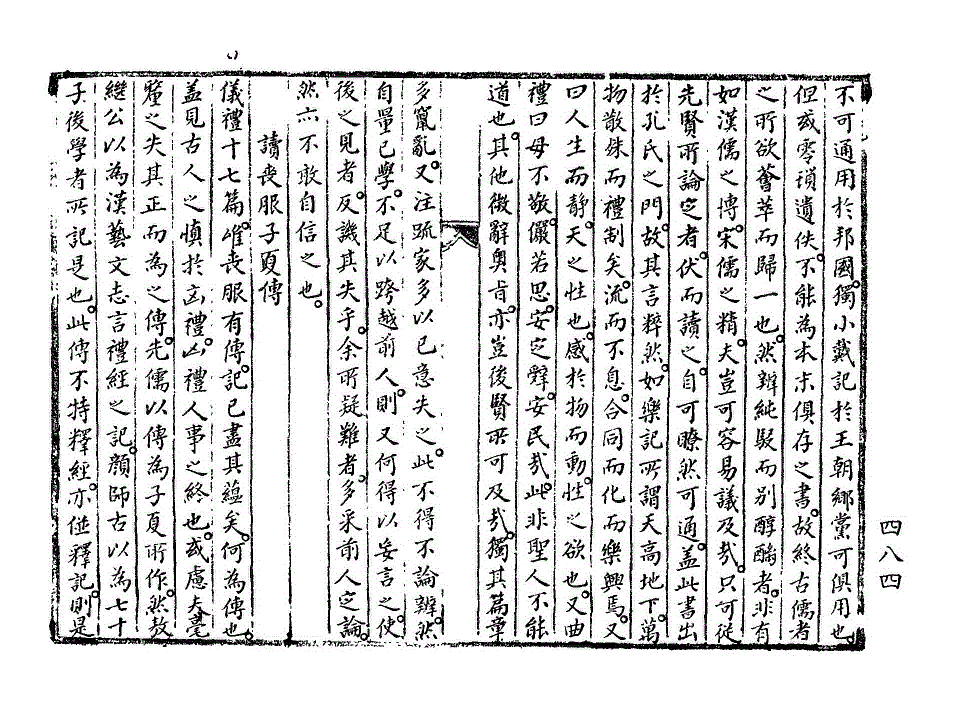 不可通用于邦国。独小戴记于王朝乡党可俱用也。但或零琐遗佚。不能为本末俱存之书。故终古儒者之所欲荟萃而归一也。然辨纯驳而别醇醨者。非有如汉儒之博。宋儒之精。夫岂可容易议及哉。只可从先贤所论定者。伏而读之。自可瞭然可通。盖此书出于孔氏之门。故其言粹然。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又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又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此非圣人不能道也。其他微辞奥旨。亦岂后贤所可及哉。独其篇章多窜乱。又注疏家多以己意失之。此不得不论辨。然自量已学。不足以跨越前人。则又何得以妄言之。使后之见者。反讥其失乎。余所疑难者。多采前人定论。然亦不敢自信之也。
不可通用于邦国。独小戴记于王朝乡党可俱用也。但或零琐遗佚。不能为本末俱存之书。故终古儒者之所欲荟萃而归一也。然辨纯驳而别醇醨者。非有如汉儒之博。宋儒之精。夫岂可容易议及哉。只可从先贤所论定者。伏而读之。自可瞭然可通。盖此书出于孔氏之门。故其言粹然。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又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又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此非圣人不能道也。其他微辞奥旨。亦岂后贤所可及哉。独其篇章多窜乱。又注疏家多以己意失之。此不得不论辨。然自量已学。不足以跨越前人。则又何得以妄言之。使后之见者。反讥其失乎。余所疑难者。多采前人定论。然亦不敢自信之也。读丧服子夏传
仪礼十七篇。唯丧服有传。记已尽其蕴矣。何为传也。盖见古人之慎于凶礼。凶礼人事之终也。或虑夫毫釐之失其正而为之传。先儒以传为子夏所作。然敖继公以为汉艺文志言礼经之记。颜师古以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是也。此传不特释经。亦并释记。则是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5H 页
 作传者。又在作记者之后明矣。余尝读之。其发明礼意者虽精切。而间有龃龉不合者。有篇策错迂者。有不知而释者。有错看而训者。郑康成亦有辨矣。盖经生学士互相传述。不专出于一门。故往往坏乱如此。夫传者传经也。自为一编。编于经后。自孔子传易之彖象。丘明之传春秋。至于毛苌之传诗。莫不皆然。故离经而读之。自成文理。至若丧服传不然。类附经文而成者。如经父为长子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经为人后者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经母为长子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究此数说。传若不附于经而自为一编则不辞矣。夫割传而附经。自马融始。费直之属。纷纷效之。窃疑此传之作。亦在马融后耳。古之说礼者。皆有师说。而后儒乃能荟萃诸说。就经下而续之。如卫宏之作诗序也。不然一章之内。何屡称传曰也。传曰者。非古者诸儒之传说乎。盖孔子之门。游夏最习于礼。传者托而为之名也。余具摘其疵颣于下。
作传者。又在作记者之后明矣。余尝读之。其发明礼意者虽精切。而间有龃龉不合者。有篇策错迂者。有不知而释者。有错看而训者。郑康成亦有辨矣。盖经生学士互相传述。不专出于一门。故往往坏乱如此。夫传者传经也。自为一编。编于经后。自孔子传易之彖象。丘明之传春秋。至于毛苌之传诗。莫不皆然。故离经而读之。自成文理。至若丧服传不然。类附经文而成者。如经父为长子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经为人后者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经母为长子下。即传曰何以三年也。究此数说。传若不附于经而自为一编则不辞矣。夫割传而附经。自马融始。费直之属。纷纷效之。窃疑此传之作。亦在马融后耳。古之说礼者。皆有师说。而后儒乃能荟萃诸说。就经下而续之。如卫宏之作诗序也。不然一章之内。何屡称传曰也。传曰者。非古者诸儒之传说乎。盖孔子之门。游夏最习于礼。传者托而为之名也。余具摘其疵颣于下。经。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谓有地者也。近臣君服斯服。(敖继公曰经唯言公卿大夫尔。而传以有地者释之。则无地者其服不如是乎。近臣君服斯服。乃诸侯之近臣从君服者也。传言于此。似非其类。○方苞曰小记近臣君服斯服矣。谓税服也。服问近臣唯君所服服也。谓君之母。非夫人者也。非是则于君丧。未有嗣君服。而臣不服也。此衍文。)案郑贾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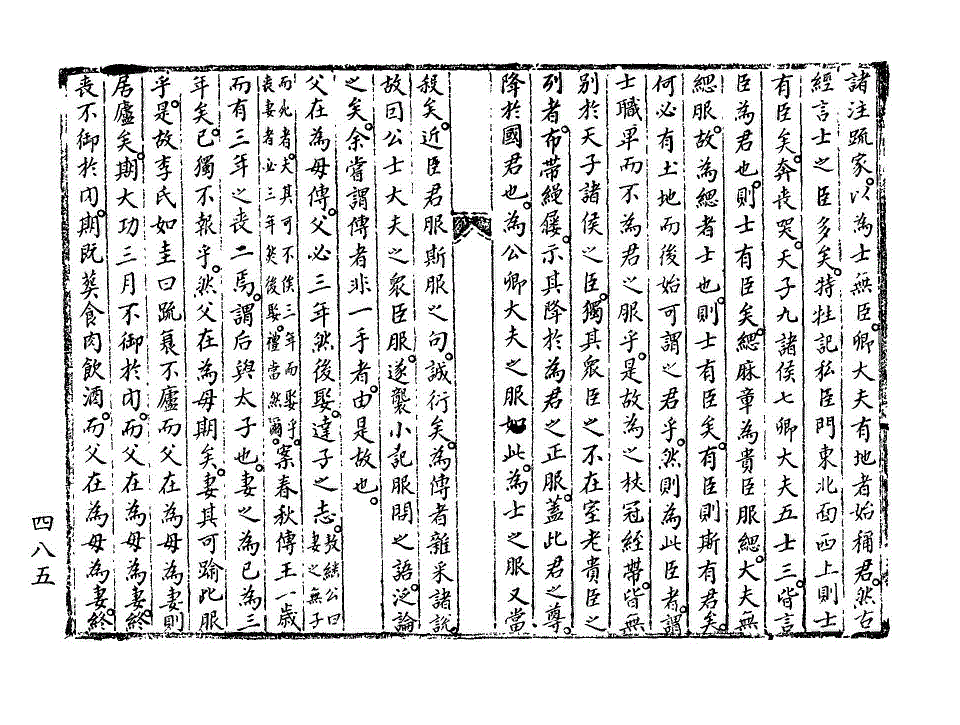 诸注疏家。以为士无臣。卿大夫有地者始称君。然古经言士之臣多矣。特牲记私臣门东北面西上则士有臣矣。奔丧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皆言臣为君也。则士有臣矣。缌麻章为贵臣服缌。大夫无缌服。故为缌者士也。则士有臣矣。有臣则斯有君矣。何必有土地而后始可谓之君乎。然则为此臣者。谓士职卑而不为君之服乎。是故为之杖冠绖带。皆无别于天子诸侯之臣。独其众臣之不在室老贵臣之列者。布带绳屦。示其降于为君之正服。盖此君之尊。降于国君也。为公卿大夫之服如此。为士之服又当杀矣。近臣君服斯服之句。诚衍矣。为传者杂采诸说。故因公士大夫之众臣服。遂袭小记服问之语。泛论之矣。余尝谓传者非一手者。由是故也。
诸注疏家。以为士无臣。卿大夫有地者始称君。然古经言士之臣多矣。特牲记私臣门东北面西上则士有臣矣。奔丧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皆言臣为君也。则士有臣矣。缌麻章为贵臣服缌。大夫无缌服。故为缌者士也。则士有臣矣。有臣则斯有君矣。何必有土地而后始可谓之君乎。然则为此臣者。谓士职卑而不为君之服乎。是故为之杖冠绖带。皆无别于天子诸侯之臣。独其众臣之不在室老贵臣之列者。布带绳屦。示其降于为君之正服。盖此君之尊。降于国君也。为公卿大夫之服如此。为士之服又当杀矣。近臣君服斯服之句。诚衍矣。为传者杂采诸说。故因公士大夫之众臣服。遂袭小记服问之语。泛论之矣。余尝谓传者非一手者。由是故也。父在为母传。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敖继公曰妻之无子而死者。夫其可不俟三年而娶乎。丧妻者必三年然后娶。礼当然尔。)案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太子也。妻之为己为三年矣。己独不报乎。然父在为母期矣。妻其可踰此服乎。是故李氏如圭曰疏衰不庐而父在为母为妻则居庐矣。期大功三月不御于内。而父在为母为妻。终丧不御于内。期既葬食肉饮酒。而父在为母为妻。终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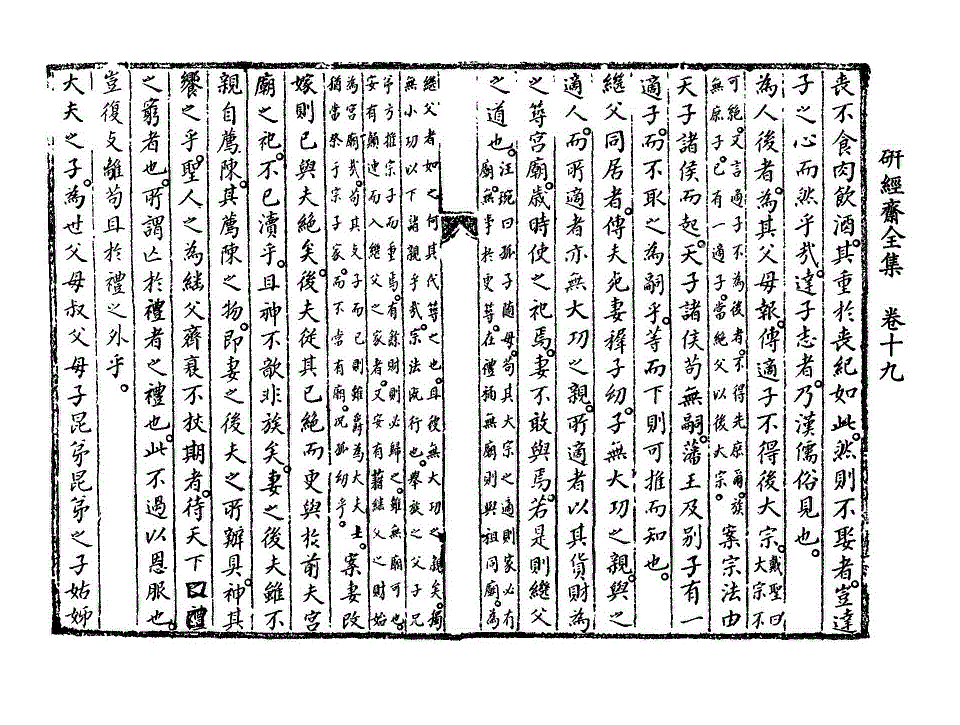 丧不食肉饮酒。其重于丧纪如此。然则不娶者。岂达子之心而然乎哉。达子志者。乃汉儒俗见也。
丧不食肉饮酒。其重于丧纪如此。然则不娶者。岂达子之心而然乎哉。达子志者。乃汉儒俗见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适子不得后大宗。(戴圣曰大宗不可绝。又言适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尔。族无庶子。己有一适子。当绝父以后大宗。)案宗法由天子诸侯而起。天子诸侯苟无嗣。藩王及别子有一适子。而不取之为嗣乎。等而下则可推而知也。
继父同居者。传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而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妻不敢与焉。若是则继父之道也。(汪琬曰孤子随母。苟其大宗之适则家必有庙。无事于更筑。在礼祢无庙则与祖同庙。为继父者如之何其代筑之也。且彼无大功之亲矣。独无小功以下诸亲乎哉。宗法既行也。举族之父子兄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馀财则必归之。虽无庙可也。安有颠连而入继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继父之财始为宫庙哉。苟其支子而已则虽爵为大夫士。犹当祭于宗子家。而不当有庙。况孤幼乎。)案妻改嫁则已与夫绝矣。后夫从其已绝而更与于前夫宫庙之祀。不已渎乎。且神不歆非族矣。妻之后夫虽不亲自荐陈。其荐陈之物。即妻之后夫之所办具。神其飨之乎。圣人之为继父齐衰不杖期者。待天下之穷者也。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此不过以恩服也。岂复支离苟且于礼之外乎。
大夫之子。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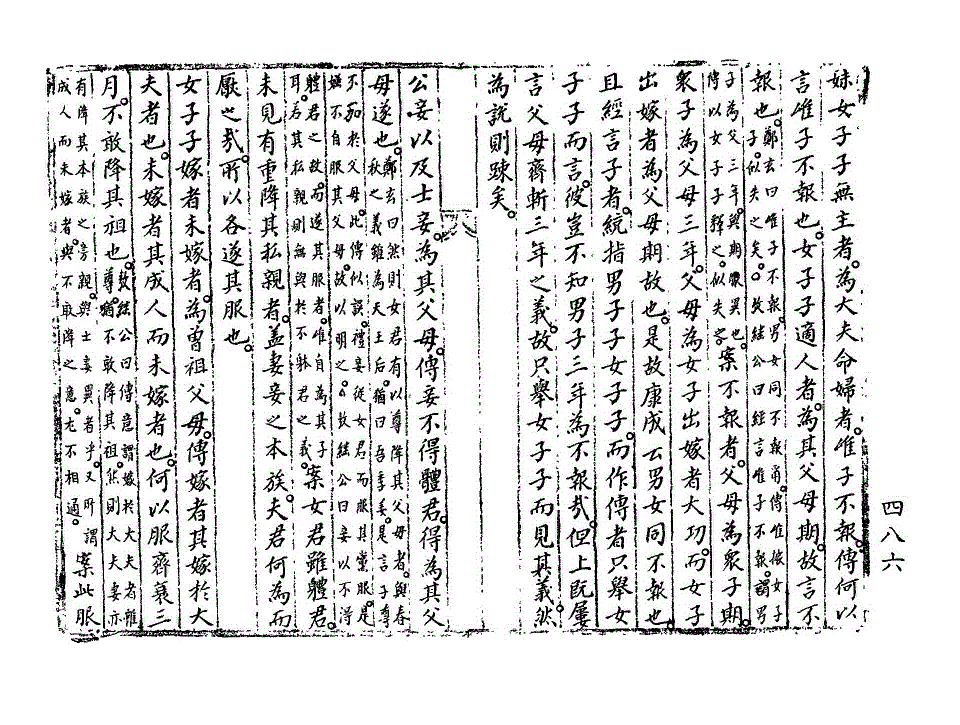 妹女子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唯子不报。传何以言唯子不报也。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郑玄曰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唯据女子子。似失之矣。○敖继公曰经言唯子不报。谓男子为父三年。与期服异也。传以女子子释之。似失之。)案不报者。父母为众子期。众子为父母三年。父母为女子出嫁者大功。而女子出嫁者为父母期故也。是故康成云男女同不报也。且经言子者。统指男子子女子子。而作传者只举女子子而言。彼岂不知男子三年为不报哉。但上既屡言父母齐斩三年之义。故只举女子子而见其义。然为说则疏矣。
妹女子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唯子不报。传何以言唯子不报也。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郑玄曰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唯据女子子。似失之矣。○敖继公曰经言唯子不报。谓男子为父三年。与期服异也。传以女子子释之。似失之。)案不报者。父母为众子期。众子为父母三年。父母为女子出嫁者大功。而女子出嫁者为父母期故也。是故康成云男女同不报也。且经言子者。统指男子子女子子。而作传者只举女子子而言。彼岂不知男子三年为不报哉。但上既屡言父母齐斩三年之义。故只举女子子而见其义。然为说则疏矣。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郑玄曰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礼妾从女君而服其党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敖继公曰妾以不得体君之故。而遂其服者。唯自为其子耳。若其私亲则无与于不体君之义。)案女君虽体君。未见有重降其私亲者。盖妻妾之本族。夫君何为而厌之哉。所以各遂其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传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齐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敖继公曰传意谓嫁于大夫者虽尊。犹不敢降其祖。然则大夫妻亦有降其本族之旁亲。与士妻异者乎。又所谓成人而未嫁者。与不敢降之意。尤不相通。)案此服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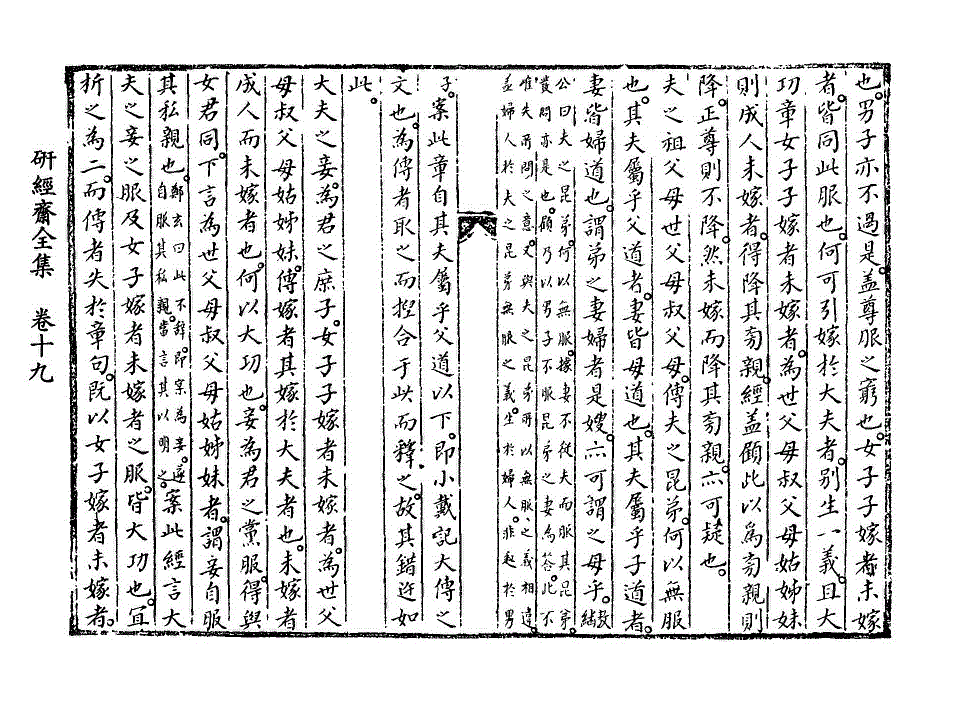 也。男子亦不过是。盖尊服之穷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皆同此服也。何可引嫁于大夫者。别生一义。且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则成人未嫁者。得降其旁亲。经盖顾此以为旁亲则降。正尊则不降。然未嫁而降其旁亲。亦可疑也。
也。男子亦不过是。盖尊服之穷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皆同此服也。何可引嫁于大夫者。别生一义。且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则成人未嫁者。得降其旁亲。经盖顾此以为旁亲则降。正尊则不降。然未嫁而降其旁亲。亦可疑也。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传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敖继公曰夫之昆弟。何以无服。据妻不从夫而服其昆弟。发问亦是也。顾乃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为答。此不唯失所问之意。又与夫之昆弟所以无服之义相违。盖妇人于夫之昆弟无服之义。生于妇人。非起于男子。)案此章自其夫属乎父道以下。即小戴记大传之文也。为传者取之而捏合于此而释之。故其错迕如此。
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传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郑玄曰此不辞。即宲为妾。遂自服其私亲。当言其以明之。)案此经言大夫之妾之服及女子嫁者未嫁者之服。皆大功也。宜折之为二。而传者失于章句。既以女子嫁者未嫁者。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九 第 487L 页
 并于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章世父母以下。更无所属。故并以为大夫妾之服殊误。小功章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经有明文。此女子子之嫁者。又可以大夫之妾贯之乎。
并于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章世父母以下。更无所属。故并以为大夫妾之服殊误。小功章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经有明文。此女子子之嫁者。又可以大夫之妾贯之乎。从父昆弟之子之长殇。昆弟之孙之长殇。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妻。传长殇中殇降一等。下殇降二等。又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中从下。(方苞曰传但言其中从上者。若中从下者。丈夫为小功之下殇无服矣。故不著也。此疑当在殇小
记大夫吊于命妇锡衰。传锡者何也。麻之有锡者也。(敖继公曰有锡。疑滑易二字之误。盖二字各有似也。司服职注郑司农云锡麻之滑易者也。其据此记未误之文与。)案有锡。即传写之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