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x 页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文二○记事
文二○记事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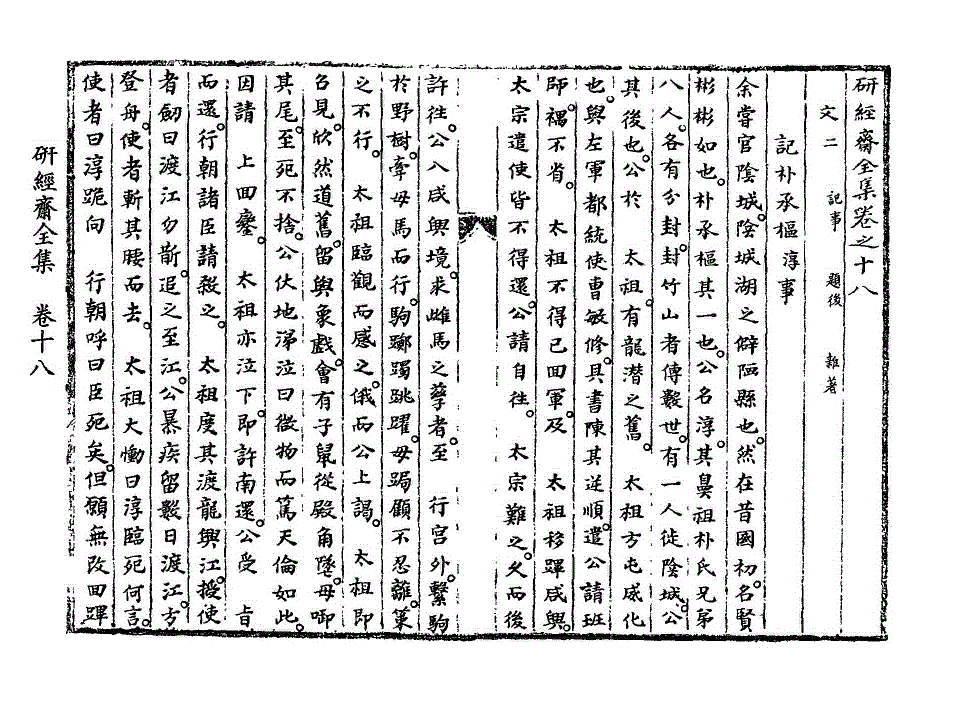 记朴承枢(淳)事
记朴承枢(淳)事余尝官阴城。阴城湖之僻陋县也。然在昔国初。名贤彬彬如也。朴承枢其一也。公名淳。其鼻祖朴氏兄弟八人。各有分封。封竹山者传数世。有一人徙阴城。公其后也。公于 太祖。有龙潜之旧。 太祖方屯威化也。与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具书陈其逆顺。遣公请班师。祦不省。 太祖不得已回军。及 太祖移跸咸兴。太宗遣使皆不得还。公请自往。 太宗难之。久而后许往。公入咸兴境。求雌马之孳者。至 行宫外。击驹于野树。牵母马而行。驹踯躅跳跃。母跼顾不忍离。策之不行。 太祖临观而感之。俄而公上谒。 太祖即召见。欣然道旧。留与象戏。会有子鼠从殿角坠。母衔其尾。至死不舍。公伏地涕泣曰微物而笃天伦如此。因请 上回銮。 太祖亦泣下。即许南还。公受 旨而还。行朝诸臣请杀之。 太祖度其渡龙兴江。授使者剑曰渡江勿斮。追之至江。公暴疾留数日渡江。方登舟。使者斩其腰而去。 太祖大恸曰淳临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 行朝呼曰臣死矣。但愿无改回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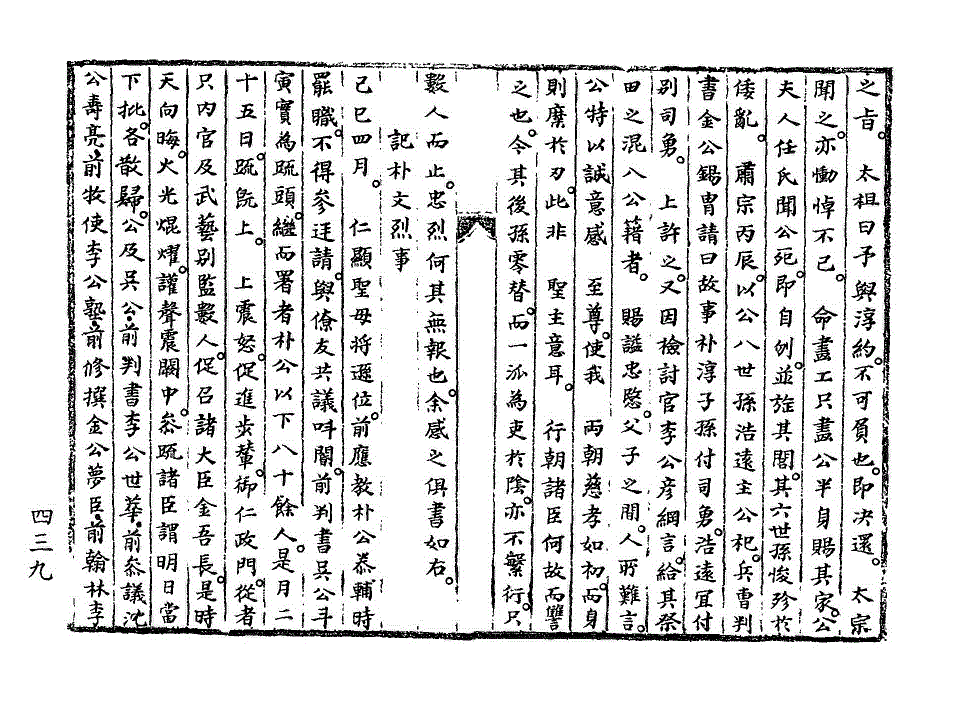 之旨。 太祖曰予与淳约。不可负也。即决还。 太宗闻之。亦恸悼不已。 命画工只画公半身赐其家。公夫人任氏闻公死。即自刎。并㫌其闾。其六世孙悛殄于倭乱。 肃宗丙辰。以公八世孙浩远主公祀。兵曹判书金公锡胄请曰故事朴淳子孙付司勇。浩远宜付别司勇。 上许之。又因检讨官李公彦纲言。给其祭田之混入公籍者。 赐谥忠悯。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特以诚意感 至尊。使我 两朝慈孝如初。而身则糜于刃。此非 圣主意耳。 行朝诸臣何故而雠之也。今其后孙零替。而一派为吏于阴。亦不繁衍。只数人而止。忠烈何其无报也。余感之俱书如右。
之旨。 太祖曰予与淳约。不可负也。即决还。 太宗闻之。亦恸悼不已。 命画工只画公半身赐其家。公夫人任氏闻公死。即自刎。并㫌其闾。其六世孙悛殄于倭乱。 肃宗丙辰。以公八世孙浩远主公祀。兵曹判书金公锡胄请曰故事朴淳子孙付司勇。浩远宜付别司勇。 上许之。又因检讨官李公彦纲言。给其祭田之混入公籍者。 赐谥忠悯。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特以诚意感 至尊。使我 两朝慈孝如初。而身则糜于刃。此非 圣主意耳。 行朝诸臣何故而雠之也。今其后孙零替。而一派为吏于阴。亦不繁衍。只数人而止。忠烈何其无报也。余感之俱书如右。记朴文烈事
己巳四月。 仁显圣母将逊位。前应教朴公泰辅时罢职。不得参廷请。与僚友共议叫阍。前判书吴公斗寅实为疏头。继而署者朴公以下八十馀人。是月二十五日。疏既上。 上震怒。促进步辇。御仁政门。从者只内官及武艺别监数人。促召诸大臣金吾长。是时天向晦。火光焜耀。欢声震阙中。参疏诸臣谓明日当下批。各散归。公及吴公,前判书李公世华,前参议沈公寿亮,前牧使李公塾,前修撰金公梦臣,前翰林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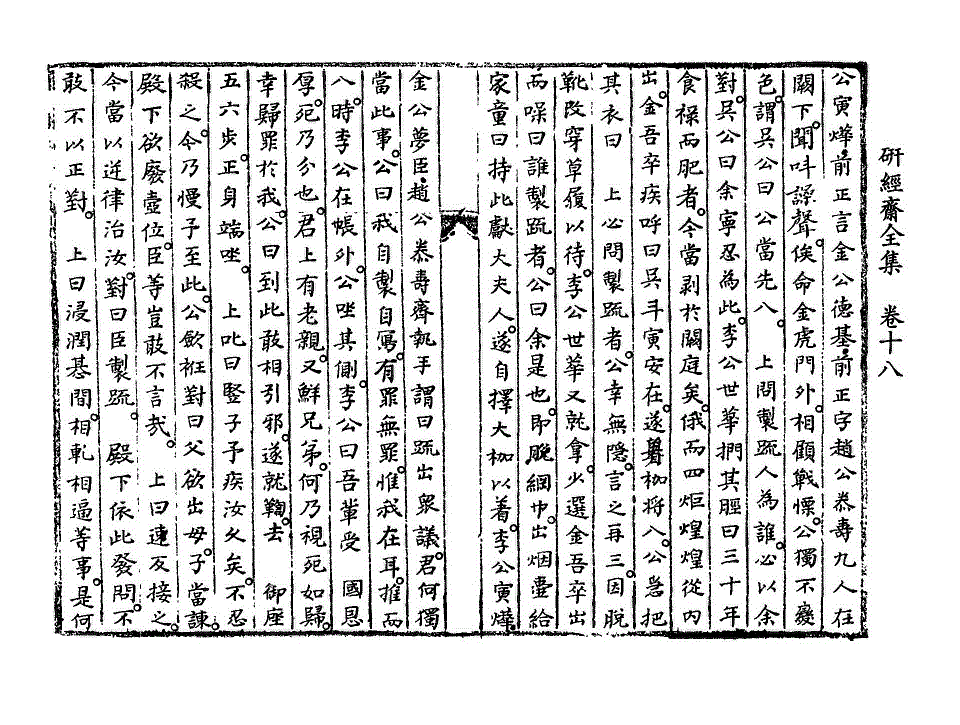 公寅烨,前正言金公德基,前正字赵公泰寿九人在阙下。闻叫噪声。俟命金虎门外。相顾战慄。公独不变色。谓吴公曰公当先入。 上问制疏人为谁。必以余对。吴公曰余宁忍为此。李公世华扪其胫曰三十年食禄而肥者。今当剥于阙庭矣。俄而四炬煌煌从内出。金吾卒疾呼曰吴斗寅安在。遂着枷将入。公急把其衣曰 上必问制疏者。公幸无隐。言之再三。因脱靴改穿草履以待。李公世华又就拿。少选金吾卒出而噪曰谁制疏者。公曰余是也。即脱网巾。出烟壶给家童曰持此献大夫人。遂自择大枷以着。李公寅烨,金公梦臣,赵公泰寿齐执手谓曰疏出众议。君何独当此事。公曰我自制自写。有罪无罪。惟我在耳。推而入。时李公在帐外。公坐其侧。李公曰吾辈受 国恩厚。死乃分也。君上有老亲。又鲜兄弟。何乃视死如归。幸归罪于我。公曰到此敢相引邪。遂就鞫。去 御座五六步。正身端坐。 上叱曰竖子予疾汝久矣。不忍杀之。今乃慢予至此。公敛衽对曰父欲出母。子当谏。殿下欲废壸位。臣等岂敢不言哉。 上曰速反接之。今当以逆律治汝。对曰臣制疏。 殿下依此发问。不敢不以正对。 上曰浸润惎间。相轧相逼等事。是何
公寅烨,前正言金公德基,前正字赵公泰寿九人在阙下。闻叫噪声。俟命金虎门外。相顾战慄。公独不变色。谓吴公曰公当先入。 上问制疏人为谁。必以余对。吴公曰余宁忍为此。李公世华扪其胫曰三十年食禄而肥者。今当剥于阙庭矣。俄而四炬煌煌从内出。金吾卒疾呼曰吴斗寅安在。遂着枷将入。公急把其衣曰 上必问制疏者。公幸无隐。言之再三。因脱靴改穿草履以待。李公世华又就拿。少选金吾卒出而噪曰谁制疏者。公曰余是也。即脱网巾。出烟壶给家童曰持此献大夫人。遂自择大枷以着。李公寅烨,金公梦臣,赵公泰寿齐执手谓曰疏出众议。君何独当此事。公曰我自制自写。有罪无罪。惟我在耳。推而入。时李公在帐外。公坐其侧。李公曰吾辈受 国恩厚。死乃分也。君上有老亲。又鲜兄弟。何乃视死如归。幸归罪于我。公曰到此敢相引邪。遂就鞫。去 御座五六步。正身端坐。 上叱曰竖子予疾汝久矣。不忍杀之。今乃慢予至此。公敛衽对曰父欲出母。子当谏。殿下欲废壸位。臣等岂敢不言哉。 上曰速反接之。今当以逆律治汝。对曰臣制疏。 殿下依此发问。不敢不以正对。 上曰浸润惎间。相轧相逼等事。是何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0L 页
 语也。公逐行注释曰某言指此。某言指彼。凡人有一妻一妾。而偏爱其妾则身不修而家不齐。今 殿下嬖幸后宫。所言皆从。臣等恐蔽天聪也。 上曰以予惑于娼妾。做作妄言。如李广汉者耶。即命罗卒以索系项接于胸。不得屈伸。拷掠甚严。左右督刑之声震地。公容貌不改。 上厉声曰洪致祥以诬上而死。汝不知乎。对曰洪致祥微谏而死。臣疏出于舆论。非致祥可匹也。夫妇人伦之始也。愚妇愚夫。犹知义重。况国君乎。 殿下以元子诞生于后宫。故始有此绿衣之计。臣谓 殿下必入浸润之谗。忧不能已也。 上怒甚不能成声曰汝不服未。汝恶过于金弘郁也。命以杖击口。且遍筑之。肌肤片片剥落。受刑已二次。流血遍身。衣裳尽湿。 上又促压膝具。公曰臣之捐身固分也。 殿下何为此亡国之祸也。臣以世臣。义同休戚。不敢不言。 上顾谓史臣勿书。于是扛沙数石压其膝上。加一大板。罗卒六人分蹋两端凡十三。如是者再。公辞令如旧。 上尤怒曰顽梗如此。宜辱之及予。又问梦中事是何言也。对曰此在 殿下备忘记。 上曰以余为妄言者耶。对曰宫中事。非臣所知。然 殿下摘发微事。以成大罪。岂非过耶。 上怒甚
语也。公逐行注释曰某言指此。某言指彼。凡人有一妻一妾。而偏爱其妾则身不修而家不齐。今 殿下嬖幸后宫。所言皆从。臣等恐蔽天聪也。 上曰以予惑于娼妾。做作妄言。如李广汉者耶。即命罗卒以索系项接于胸。不得屈伸。拷掠甚严。左右督刑之声震地。公容貌不改。 上厉声曰洪致祥以诬上而死。汝不知乎。对曰洪致祥微谏而死。臣疏出于舆论。非致祥可匹也。夫妇人伦之始也。愚妇愚夫。犹知义重。况国君乎。 殿下以元子诞生于后宫。故始有此绿衣之计。臣谓 殿下必入浸润之谗。忧不能已也。 上怒甚不能成声曰汝不服未。汝恶过于金弘郁也。命以杖击口。且遍筑之。肌肤片片剥落。受刑已二次。流血遍身。衣裳尽湿。 上又促压膝具。公曰臣之捐身固分也。 殿下何为此亡国之祸也。臣以世臣。义同休戚。不敢不言。 上顾谓史臣勿书。于是扛沙数石压其膝上。加一大板。罗卒六人分蹋两端凡十三。如是者再。公辞令如旧。 上尤怒曰顽梗如此。宜辱之及予。又问梦中事是何言也。对曰此在 殿下备忘记。 上曰以余为妄言者耶。对曰宫中事。非臣所知。然 殿下摘发微事。以成大罪。岂非过耶。 上怒甚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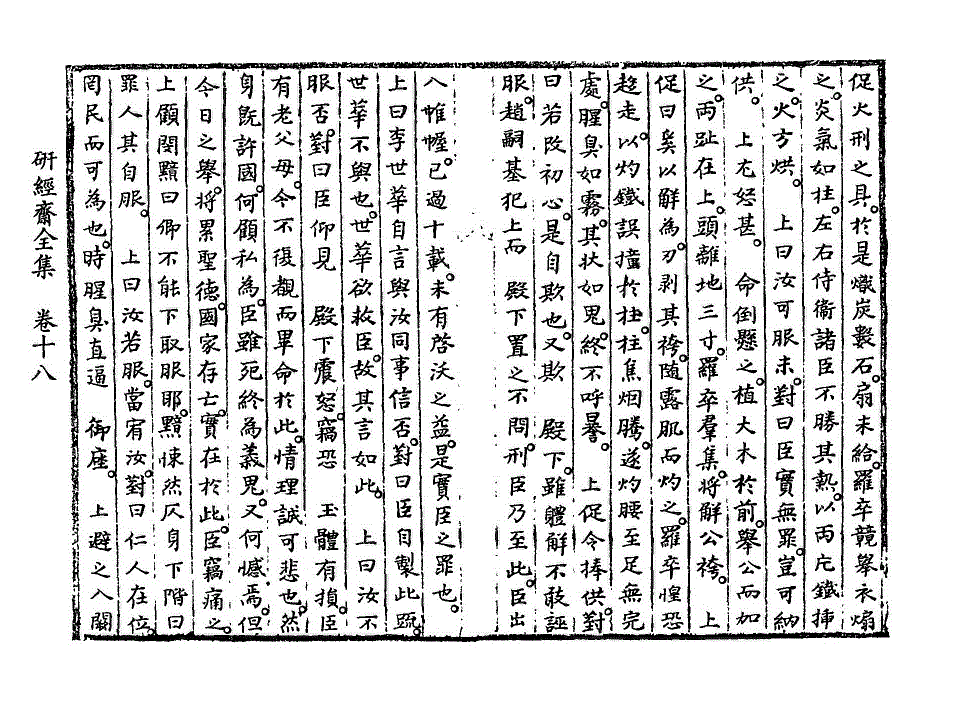 促火刑之具。于是炽炭数石。扇未给。罗卒竞举衣煽之。炎气如柱。左右侍卫诸臣不胜其热。以两片铁插之。火方烘。 上曰汝可服未。对曰臣实无罪。岂可纳供。 上尤怒甚。 命倒悬之。植大木于前。举公而加之。两趾在上。头离地三寸。罗卒群集。将解公裤。 上促曰奚以解为。刃剥其裤。随露肌而灼之。罗卒惶恐趍走。以灼铁误撞于柱。柱焦烟腾。遂灼腰至足无完处。腥臭如雾。其状如鬼。终不呼謈。 上促令捧供。对曰若改初心。是自欺也。又欺 殿下。虽体解不敢诬服。赵嗣基犯上而 殿下置之不问。刑臣乃至此。臣出入帷幄。已过十载。未有启沃之益。是实臣之罪也。 上曰李世华自言与汝同事信否。对曰臣自制此疏。世华不与也。世华欲救臣。故其言如此。 上曰汝不服否。对曰臣仰见 殿下震怒。窃恐 玉体有损。臣有老父母。今不复睹而毕命于此。情理诚可悲也。然身既许国。何顾私为。臣虽死终为义鬼。又何憾焉。但今日之举。将累圣德。国家存亡。实在于此。臣窃痛之。上顾闵黯曰卿不能下取服耶。黯悚然仄身下阶曰罪人其自服。 上曰汝若服。当宥汝。对曰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时腥臭直逼 御座。 上避之入阙
促火刑之具。于是炽炭数石。扇未给。罗卒竞举衣煽之。炎气如柱。左右侍卫诸臣不胜其热。以两片铁插之。火方烘。 上曰汝可服未。对曰臣实无罪。岂可纳供。 上尤怒甚。 命倒悬之。植大木于前。举公而加之。两趾在上。头离地三寸。罗卒群集。将解公裤。 上促曰奚以解为。刃剥其裤。随露肌而灼之。罗卒惶恐趍走。以灼铁误撞于柱。柱焦烟腾。遂灼腰至足无完处。腥臭如雾。其状如鬼。终不呼謈。 上促令捧供。对曰若改初心。是自欺也。又欺 殿下。虽体解不敢诬服。赵嗣基犯上而 殿下置之不问。刑臣乃至此。臣出入帷幄。已过十载。未有启沃之益。是实臣之罪也。 上曰李世华自言与汝同事信否。对曰臣自制此疏。世华不与也。世华欲救臣。故其言如此。 上曰汝不服否。对曰臣仰见 殿下震怒。窃恐 玉体有损。臣有老父母。今不复睹而毕命于此。情理诚可悲也。然身既许国。何顾私为。臣虽死终为义鬼。又何憾焉。但今日之举。将累圣德。国家存亡。实在于此。臣窃痛之。上顾闵黯曰卿不能下取服耶。黯悚然仄身下阶曰罪人其自服。 上曰汝若服。当宥汝。对曰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时腥臭直逼 御座。 上避之入阙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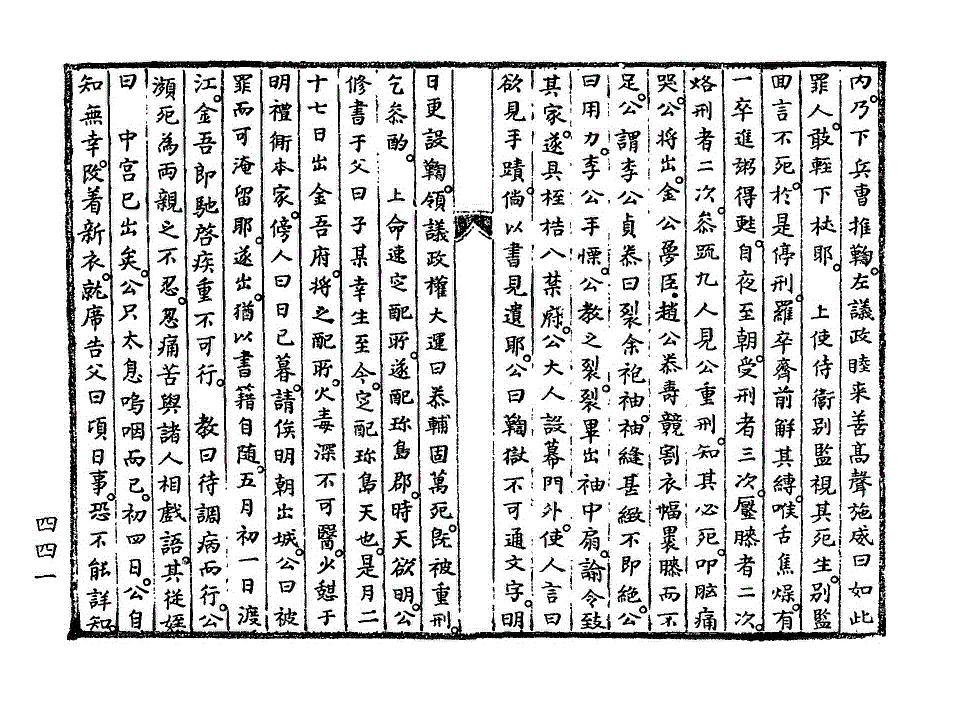 内。乃下兵曹推鞫。左议政睦来善高声施威曰如此罪人。敢轻下杖耶。 上使侍卫别监视其死生。别监回言不死。于是停刑。罗卒齐前解其缚。喉舌焦燥。有一卒进粥得苏。自夜至朝。受刑者三次。压膝者二次。烙刑者二次。参疏九人见公重刑。知其必死。叩胸痛哭。公将出。金公梦臣,赵公泰寿竞割衣幅裹膝而不足。公谓李公贞泰曰裂余袍袖。袖缝甚致不即绝。公曰用力。李公手慄。公教之裂。裂毕出袖中扇。谕令致其家。遂具桎梏入禁府。公大人设幕门外。使人言曰欲见手迹。倘以书见遗耶。公曰鞫狱不可通文字。明日更设鞫。领议政权大运曰泰辅固万死。既被重刑。乞参酌。 上命速定配所。遂配珍岛郡。时天欲明。公修书于父曰子某幸生至今。定配珍岛天也。是月二十七日出金吾府。将之配所。火毒深不可医。少憩于明礼衕本家。傍人曰日已暮。请俟明朝出城。公曰被罪而可淹留耶。遂出。犹以书籍自随。五月初一日渡江。金吾郎驰启疾重不可行。 教曰待调病而行。公濒死为两亲之不忍。忍痛苦与诸人相戏语。其从侄曰 中宫已出矣。公只太息呜咽而已。初四日。公自知无幸。改着新衣。就席告父曰顷日事。恐不能详知。
内。乃下兵曹推鞫。左议政睦来善高声施威曰如此罪人。敢轻下杖耶。 上使侍卫别监视其死生。别监回言不死。于是停刑。罗卒齐前解其缚。喉舌焦燥。有一卒进粥得苏。自夜至朝。受刑者三次。压膝者二次。烙刑者二次。参疏九人见公重刑。知其必死。叩胸痛哭。公将出。金公梦臣,赵公泰寿竞割衣幅裹膝而不足。公谓李公贞泰曰裂余袍袖。袖缝甚致不即绝。公曰用力。李公手慄。公教之裂。裂毕出袖中扇。谕令致其家。遂具桎梏入禁府。公大人设幕门外。使人言曰欲见手迹。倘以书见遗耶。公曰鞫狱不可通文字。明日更设鞫。领议政权大运曰泰辅固万死。既被重刑。乞参酌。 上命速定配所。遂配珍岛郡。时天欲明。公修书于父曰子某幸生至今。定配珍岛天也。是月二十七日出金吾府。将之配所。火毒深不可医。少憩于明礼衕本家。傍人曰日已暮。请俟明朝出城。公曰被罪而可淹留耶。遂出。犹以书籍自随。五月初一日渡江。金吾郎驰启疾重不可行。 教曰待调病而行。公濒死为两亲之不忍。忍痛苦与诸人相戏语。其从侄曰 中宫已出矣。公只太息呜咽而已。初四日。公自知无幸。改着新衣。就席告父曰顷日事。恐不能详知。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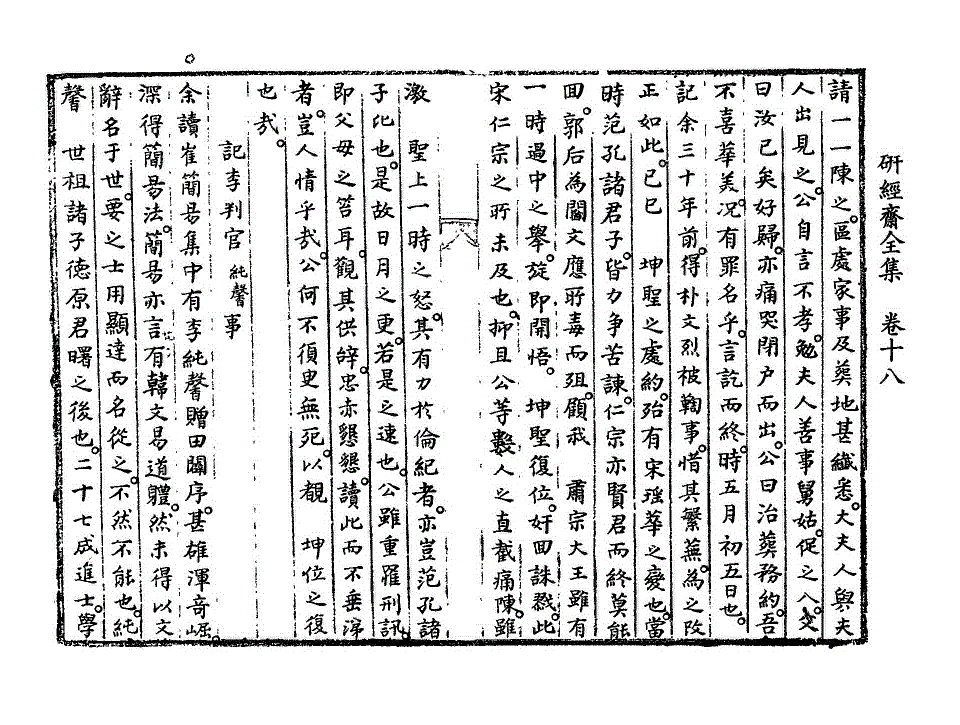 请一一陈之。区处家事及葬地甚纤悉。大夫人与夫人出见之。公自言不孝。勉夫人善事舅姑。促之入。父曰汝已矣好归。亦痛哭闭户而出。公曰治葬务约。吾不喜华美。况有罪名乎。言讫而终。时五月初五日也。
请一一陈之。区处家事及葬地甚纤悉。大夫人与夫人出见之。公自言不孝。勉夫人善事舅姑。促之入。父曰汝已矣好归。亦痛哭闭户而出。公曰治葬务约。吾不喜华美。况有罪名乎。言讫而终。时五月初五日也。记余三十年前。得朴文烈被鞫事。惜其繁芜。为之改正如此。己巳 坤圣之处约。殆有宋瑶华之变也。当时范孔诸君子。皆力争苦谏。仁宗亦贤君而终莫能回。郭后为阎文应所毒而殂。顾我 肃宗大王虽有一时过中之举。旋即开悟。 坤圣复位。奸回诛戮。此宋仁宗之所未及也。抑且公等数人之直截痛陈。虽激 圣上一时之怒。其有力于伦纪者。亦岂范孔诸子比也。是故日月之更。若是之速也。公虽重罹刑讯。即父母之笞耳。观其供辞。忠赤恳恳。读此而不垂涕者。岂人情乎哉。公何不须臾无死。以睹 坤位之复也哉。
记李判官(纯馨)事
余读崔简易集中有李纯馨赠田辟序。甚雄浑奇崛。深得简易法。简易亦言有韩文易道体。然未得以文辞名于世。要之士用显达而名从之。不然不能也。纯馨 世祖诸子德原君曙之后也。二十七成进士。学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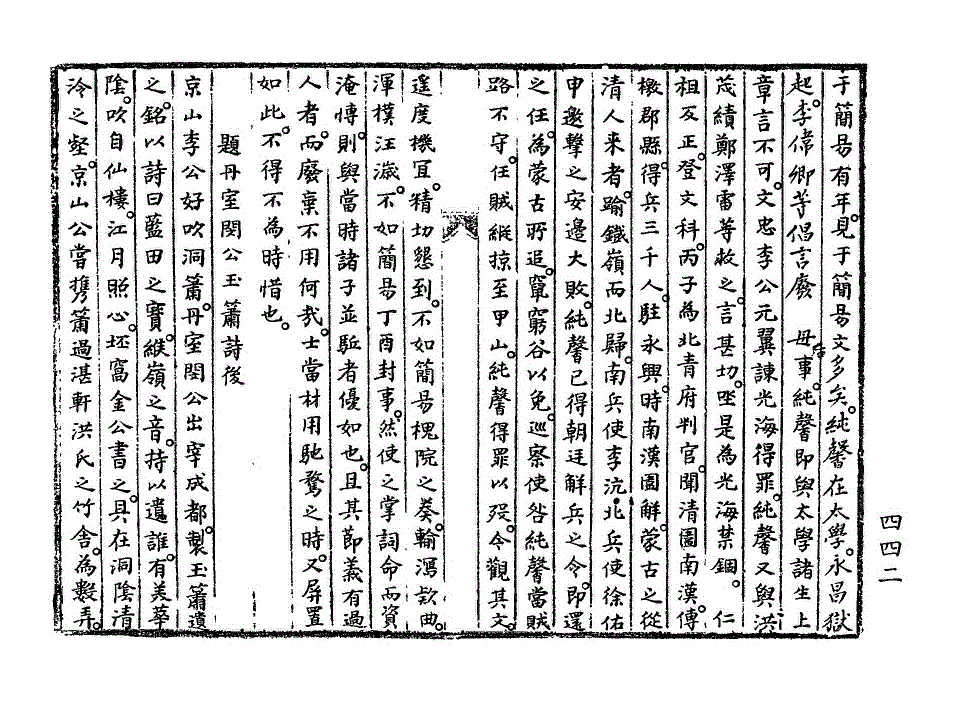 于简易有年。见于简易文多矣。纯馨在太学。永昌狱起。李伟卿等倡言废 母后事。纯馨即与太学诸生上章言不可。文忠李公元翼谏光海得罪。纯馨又与洪茂绩郑泽雷等救之。言甚切。坐是为光海禁锢。 仁祖反正。登文科。丙子为北青府判官。闻清围南汉。传檄郡县。得兵三千人。驻永兴。时南汉围解。蒙古之从清人来者。踰铁岭而北归。南兵使李沆,北兵使徐佑申邀击之安边大败。纯馨已得朝廷解兵之令。即还之任。为蒙古所追。窜穷谷以免。巡察使咎纯馨当贼路不守。任贼纵掠至甲山。纯馨得罪以殁。今观其文。遥度机宜。精切恳到。不如简易槐院之奏。输泻款曲。浑朴汪濊。不如简易丁酉封事。然使之掌词命而资淹博。则与当时诸子并驱者优如也。且其节义有过人者。而废弃不用何哉。士当材用驰骛之时。又屏置如此。不得不为时惜也。
于简易有年。见于简易文多矣。纯馨在太学。永昌狱起。李伟卿等倡言废 母后事。纯馨即与太学诸生上章言不可。文忠李公元翼谏光海得罪。纯馨又与洪茂绩郑泽雷等救之。言甚切。坐是为光海禁锢。 仁祖反正。登文科。丙子为北青府判官。闻清围南汉。传檄郡县。得兵三千人。驻永兴。时南汉围解。蒙古之从清人来者。踰铁岭而北归。南兵使李沆,北兵使徐佑申邀击之安边大败。纯馨已得朝廷解兵之令。即还之任。为蒙古所追。窜穷谷以免。巡察使咎纯馨当贼路不守。任贼纵掠至甲山。纯馨得罪以殁。今观其文。遥度机宜。精切恳到。不如简易槐院之奏。输泻款曲。浑朴汪濊。不如简易丁酉封事。然使之掌词命而资淹博。则与当时诸子并驱者优如也。且其节义有过人者。而废弃不用何哉。士当材用驰骛之时。又屏置如此。不得不为时惜也。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文二○题后
题丹室闵公玉箫诗后
京山李公好吹洞箫。丹室闵公出宰成都。制玉箫遗之。铭以诗曰蓝田之宝。缑岭之音。持以遗谁。有美华阴。吹自仙楼。江月照心。坯窝金公书之。具在洞阴清泠之壑。京山公尝携箫过湛轩洪氏之竹舍。为数弄。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3H 页
 湛轩故善琴而与之为耦。又尝入金刚山。吹于歇惺楼上。寺僧惊以为仙人降楼上。夫乐者君子所以治心进德之器也。是故寻音而知心。因心而知德。疾舒奋动适于器而其音不可谐乎。欢欣恻怆中于节而其心不可治乎。廉辨贞谅充于己而其德不可进乎。是故用之郊庙之上则气和而心平。施之山林之中则伦清而理明。公深藏丘壑。虽不得为朱弦疏越之音。上助清明之治。亦得以清闲自适。伐邪涤查。以发其性命之正。殆所谓伦清而理明者欤。公少居北山下。好从先生长者游。嘐嘐斋金公素好乐律。故公从而学焉。其音正直。与俗异也。又北山素清幽深邃。泉石松籁皆足以发其境。故公益得其声音之妙。丹室公之遗之者有以夫。成都在沸流江上。素产玉。丹室公之风流遗韵。与玉之光气衣被而不绝。此君子所以比德者也。丹室公既自治其德。又采之为箫以遗公者。欲公之同其德也。岂徒为声音哉。丹室公先逝。坯窝公次之。公又不淑。君子之德。于是乎不可考矣。
湛轩故善琴而与之为耦。又尝入金刚山。吹于歇惺楼上。寺僧惊以为仙人降楼上。夫乐者君子所以治心进德之器也。是故寻音而知心。因心而知德。疾舒奋动适于器而其音不可谐乎。欢欣恻怆中于节而其心不可治乎。廉辨贞谅充于己而其德不可进乎。是故用之郊庙之上则气和而心平。施之山林之中则伦清而理明。公深藏丘壑。虽不得为朱弦疏越之音。上助清明之治。亦得以清闲自适。伐邪涤查。以发其性命之正。殆所谓伦清而理明者欤。公少居北山下。好从先生长者游。嘐嘐斋金公素好乐律。故公从而学焉。其音正直。与俗异也。又北山素清幽深邃。泉石松籁皆足以发其境。故公益得其声音之妙。丹室公之遗之者有以夫。成都在沸流江上。素产玉。丹室公之风流遗韵。与玉之光气衣被而不绝。此君子所以比德者也。丹室公既自治其德。又采之为箫以遗公者。欲公之同其德也。岂徒为声音哉。丹室公先逝。坯窝公次之。公又不淑。君子之德。于是乎不可考矣。题京山李公篆帖后
京山李公好篆籀。如岣嵝之碑石鼓之铭。商周彝鼎之文。秦碑汉隶。靡不究其蕴奥取法。务从谨严。故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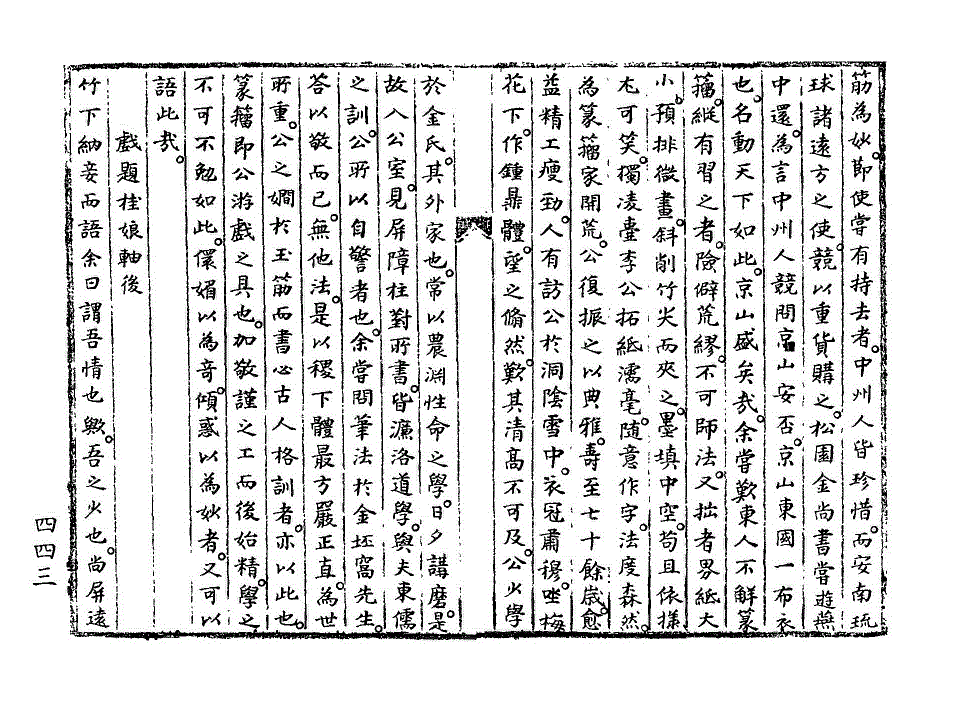 箸为妙。节使尝有持去者。中州人皆珍惜。而安南琉球诸远方之使。竞以重货购之。松园金尚书尝游燕中还。为言中州人竞问京山安否。京山东国一布衣也。名动天下如此。京山盛矣哉。余尝叹东人不解篆籀。纵有习之者。险僻荒缪。不可师法。又拙者界纸大小。预排微画。斜削竹尖而夹之。墨填中空。苟且依㨾尤可笑。独凌壶李公拓纸濡毫。随意作字。法度森然。为篆籀家开荒。公复振之以典雅。寿至七十馀岁。愈益精工瘦劲。人有访公于洞阴雪中。衣冠肃穆。坐梅花下。作钟鼎体。望之翛然。叹其清高不可及。公少学于金氏。其外家也。常以农渊性命之学。日夕讲磨。是故入公室。见屏障柱对所书。皆濂洛道学。与夫东儒之训。公所以自警者也。余尝问笔法于金坯窝先生。答以敬而已。无他法。是以稷下体最方严正直。为世所重。公之娴于玉箸而书必古人格训者。亦以此也。篆籀即公游戏之具也。加敬谨之工而后始精。学之不可不勉如此。儇媚以为奇。倾惑以为妙者。又可以语此哉。
箸为妙。节使尝有持去者。中州人皆珍惜。而安南琉球诸远方之使。竞以重货购之。松园金尚书尝游燕中还。为言中州人竞问京山安否。京山东国一布衣也。名动天下如此。京山盛矣哉。余尝叹东人不解篆籀。纵有习之者。险僻荒缪。不可师法。又拙者界纸大小。预排微画。斜削竹尖而夹之。墨填中空。苟且依㨾尤可笑。独凌壶李公拓纸濡毫。随意作字。法度森然。为篆籀家开荒。公复振之以典雅。寿至七十馀岁。愈益精工瘦劲。人有访公于洞阴雪中。衣冠肃穆。坐梅花下。作钟鼎体。望之翛然。叹其清高不可及。公少学于金氏。其外家也。常以农渊性命之学。日夕讲磨。是故入公室。见屏障柱对所书。皆濂洛道学。与夫东儒之训。公所以自警者也。余尝问笔法于金坯窝先生。答以敬而已。无他法。是以稷下体最方严正直。为世所重。公之娴于玉箸而书必古人格训者。亦以此也。篆籀即公游戏之具也。加敬谨之工而后始精。学之不可不勉如此。儇媚以为奇。倾惑以为妙者。又可以语此哉。戏题桂娘轴后
竹下纳妾而语余曰谓吾情也欤。吾之少也。尚屏远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4H 页
 艳冶。及今发种种也。岂复渝其戒也哉。吾非为情也。谓吾养也欤。吾家虽贫。衣食幸无阙乏。而妻子又足以供之。吾非为养也。事有不期成而成者。方其卜也。人有为之媒者。非吾必其卜也。方其来也。人有为之资者。非吾必其来也。诗所谓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者是也。吾将贮之于梨湖之丙舍。使之布衣短裙。操织具勤蚕麻。以佐家人之政。使之具美酝办肴核。得以邀乡里故人。酣饮怡乐。使之整饬书籍杖几之属。山房常洁净。凡所以适吾意者。吾皆预为之计者甚悉。诸公以我官桂坊时所纳。呼桂娘。而且为诗。或嘲或戒。宫商偕作。试读之怡然。又足以忘旅居之苦也。余闻其言。似若宜是姬者。姬之品行虽未可知。以竹下之贤而宜之。必顺且慧。吾且观竹下之舆儓仆隶。皆常有自得之意。其教之行于家可知。姬又将濡染之。吾知他日必以贤妾称也。诸公之诗。虽或及燕閒之私。皆善谑也。与子夜读曲之备极狎昵有异。而余不喜作艳体。然喜道人善。故亦为之诗。即轴中之一也。
艳冶。及今发种种也。岂复渝其戒也哉。吾非为情也。谓吾养也欤。吾家虽贫。衣食幸无阙乏。而妻子又足以供之。吾非为养也。事有不期成而成者。方其卜也。人有为之媒者。非吾必其卜也。方其来也。人有为之资者。非吾必其来也。诗所谓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者是也。吾将贮之于梨湖之丙舍。使之布衣短裙。操织具勤蚕麻。以佐家人之政。使之具美酝办肴核。得以邀乡里故人。酣饮怡乐。使之整饬书籍杖几之属。山房常洁净。凡所以适吾意者。吾皆预为之计者甚悉。诸公以我官桂坊时所纳。呼桂娘。而且为诗。或嘲或戒。宫商偕作。试读之怡然。又足以忘旅居之苦也。余闻其言。似若宜是姬者。姬之品行虽未可知。以竹下之贤而宜之。必顺且慧。吾且观竹下之舆儓仆隶。皆常有自得之意。其教之行于家可知。姬又将濡染之。吾知他日必以贤妾称也。诸公之诗。虽或及燕閒之私。皆善谑也。与子夜读曲之备极狎昵有异。而余不喜作艳体。然喜道人善。故亦为之诗。即轴中之一也。题海阳诗后
岁丁未秋。海阳丈自骆东之僦第。将诣杨山之先垄。骑余邻人贩柴之牛。过宿香山之精舍。先君子在都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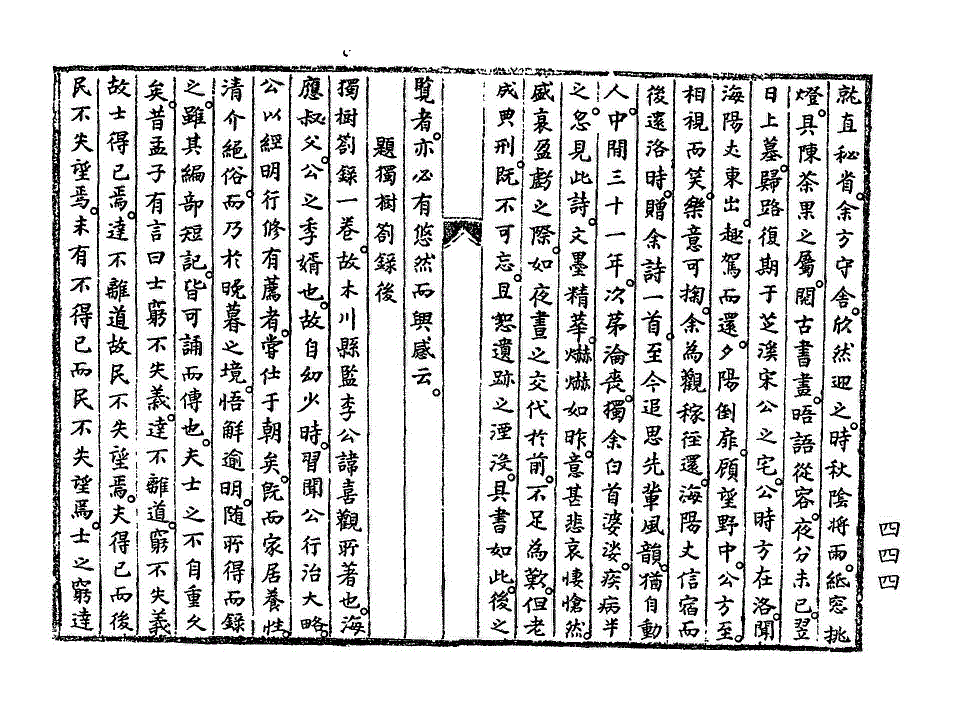 就直秘省。余方守舍。欣然迎之。时秋阴将雨。纸窗挑灯。具陈茶果之属。阅古书画。晤语从容。夜分未已。翌日上墓。归路复期于芝溪宋公之宅。公时方在洛。闻海阳丈东出。趣驾而还。夕阳倒扉。顾望野中。公方至。相视而笑。乐意可掬。余为观稼径还。海阳丈信宿而后还洛时。赠余诗一首。至今追思先辈风韵。犹自动人。中间三十一年。次第沦丧。独余白首婆娑。疾病半之。忽见此诗。文墨精华。赫赫如昨。意甚悲哀悽怆然。盛衰盈亏之际。如夜昼之交代于前。不足为叹。但老成典刑。既不可忘。且恕遗迹之湮没。具书如此。后之览者。亦必有悠然而兴感云。
就直秘省。余方守舍。欣然迎之。时秋阴将雨。纸窗挑灯。具陈茶果之属。阅古书画。晤语从容。夜分未已。翌日上墓。归路复期于芝溪宋公之宅。公时方在洛。闻海阳丈东出。趣驾而还。夕阳倒扉。顾望野中。公方至。相视而笑。乐意可掬。余为观稼径还。海阳丈信宿而后还洛时。赠余诗一首。至今追思先辈风韵。犹自动人。中间三十一年。次第沦丧。独余白首婆娑。疾病半之。忽见此诗。文墨精华。赫赫如昨。意甚悲哀悽怆然。盛衰盈亏之际。如夜昼之交代于前。不足为叹。但老成典刑。既不可忘。且恕遗迹之湮没。具书如此。后之览者。亦必有悠然而兴感云。题独树劄录后
独树劄录一卷。故木川县监李公讳喜观所著也。海应叔父。公之季婿也。故自幼少时。习闻公行治大略。公以经明行修有荐者。尝仕于朝矣。既而家居养性。清介绝俗。而乃于晚暮之境。悟解逾明。随所得而录之。虽其编部短记。皆可诵而传也。夫士之不自重久矣。昔孟子有言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夫得己而后民不失望焉。未有不得己而民不失望焉。士之穷达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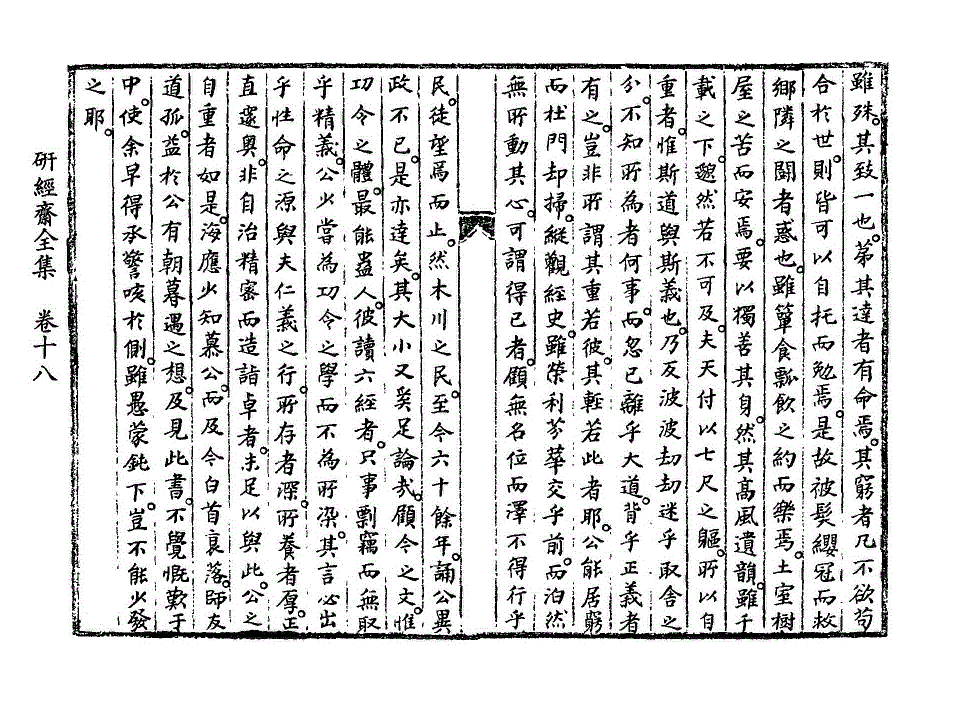 虽殊。其致一也。第其达者有命焉。其穷者凡不欲苟合于世。则皆可以自托而勉焉。是故被发缨冠而救乡邻之斗者惑也。虽箪食瓢饮之约而乐焉。土室树屋之苦而安焉。要以独善其身。然其高风遗韵。虽千载之下。邈然若不可及。夫天付以七尺之躯。所以自重者。惟斯道与斯义也。乃反波波劫劫迷乎取舍之分。不知所为者何事。而忽已离乎大道。背乎正义者有之。岂非所谓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者耶。公能居穷而杜门却扫。纵观经史。虽荣利芬华交乎前。而泊然无所动其心。可谓得己者。顾无名位而泽不得行乎民。徒望焉而止。然木川之民。至今六十馀年。诵公异政不已。是亦达矣。其大小又奚足论哉。顾今之文。惟功令之体。最能蛊人。彼读六经者。只事剽窃而无取乎精义。公少尝为功令之学而不为所染。其言必出乎性命之源与夫仁义之行。所存者深。所养者厚。正直邃奥。非自治精密而造诣卓者。未足以与此。公之自重者如是。海应少知慕公。而及今白首衰落。师友道孤。益于公有朝暮遇之想。及见此书。不觉慨叹于中。使余早得承警咳于侧。虽愚蒙钝下。岂不能少发之耶。
虽殊。其致一也。第其达者有命焉。其穷者凡不欲苟合于世。则皆可以自托而勉焉。是故被发缨冠而救乡邻之斗者惑也。虽箪食瓢饮之约而乐焉。土室树屋之苦而安焉。要以独善其身。然其高风遗韵。虽千载之下。邈然若不可及。夫天付以七尺之躯。所以自重者。惟斯道与斯义也。乃反波波劫劫迷乎取舍之分。不知所为者何事。而忽已离乎大道。背乎正义者有之。岂非所谓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者耶。公能居穷而杜门却扫。纵观经史。虽荣利芬华交乎前。而泊然无所动其心。可谓得己者。顾无名位而泽不得行乎民。徒望焉而止。然木川之民。至今六十馀年。诵公异政不已。是亦达矣。其大小又奚足论哉。顾今之文。惟功令之体。最能蛊人。彼读六经者。只事剽窃而无取乎精义。公少尝为功令之学而不为所染。其言必出乎性命之源与夫仁义之行。所存者深。所养者厚。正直邃奥。非自治精密而造诣卓者。未足以与此。公之自重者如是。海应少知慕公。而及今白首衰落。师友道孤。益于公有朝暮遇之想。及见此书。不觉慨叹于中。使余早得承警咳于侧。虽愚蒙钝下。岂不能少发之耶。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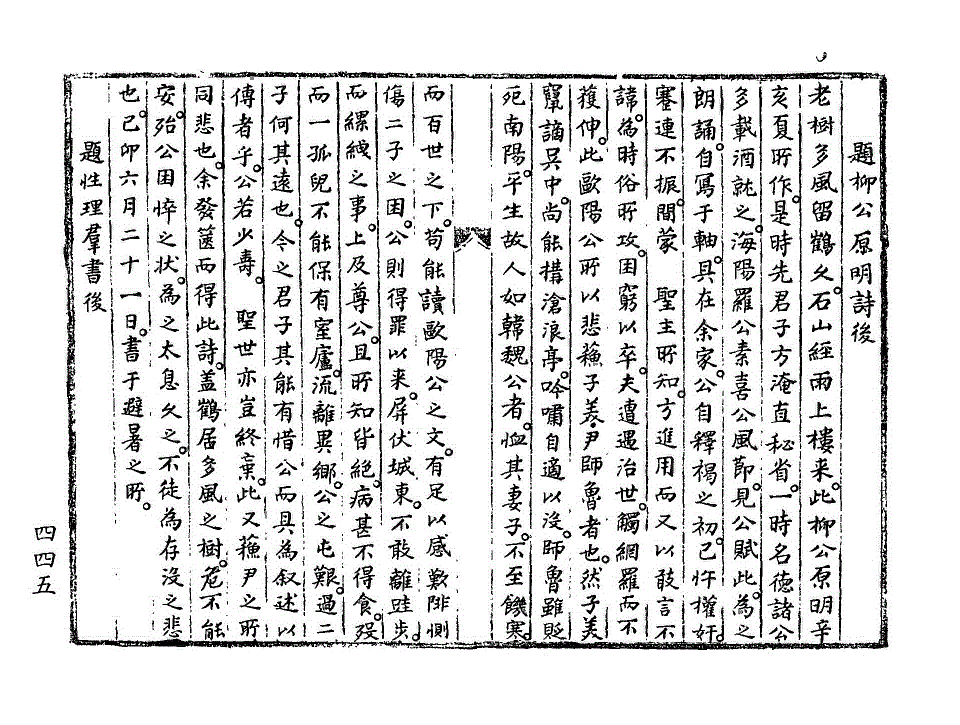 题柳公原明诗后
题柳公原明诗后老树多风留鹤久。石山经雨上楼来。此柳公原明辛亥夏所作。是时先君子方淹直秘省。一时名德诸公多载酒就之。海阳罗公素喜公风节。见公赋此。为之朗诵。自写于轴。具在余家。公自释褐之初。已忤权奸。蹇连不振。间蒙 圣主所知。方进用而又以敢言不讳。为时俗所攻。困穷以卒。夫遭遇治世。触网罗而不获伸。此欧阳公所以悲苏子美,尹师鲁者也。然子美窜谪吴中。尚能搆沧浪亭。吟啸自适以没。师鲁虽贬死南阳。平生故人如韩魏公者。恤其妻子。不至饥寒。而百世之下。苟能读欧阳公之文。有足以感叹陫恻伤二子之困。公则得罪以来。屏伏城东。不敢离跬步。而缧绁之事。上及尊公。且所知皆绝。病甚不得食。殁而一孤儿不能保有室庐。流离异乡。公之屯艰。过二子何其远也。今之君子其能有惜公而具为叙述以传者乎。公若少寿。 圣世亦岂终弃。此又苏尹之所同悲也。余发箧而得此诗。盖鹤居多风之树。危不能安。殆公困悴之状。为之太息久之。不徒为存没之悲也。己卯六月二十一日。书于避暑之所。
题性理群书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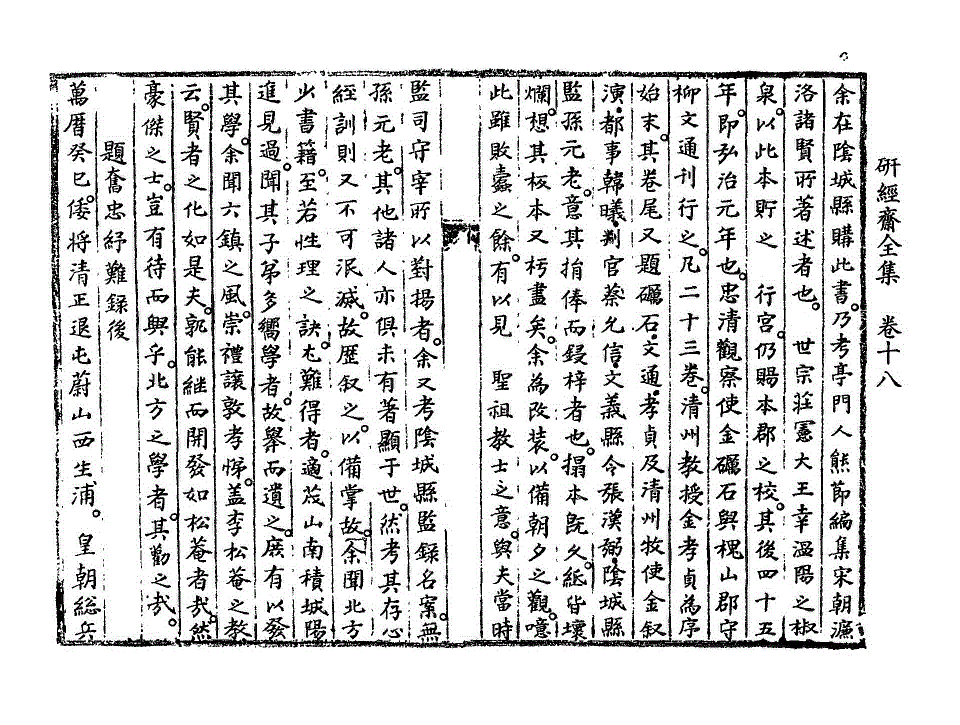 余在阴城县购此书。乃考亭门人熊节编集宋朝濂洛诸贤所著述者也。 世宗庄宪大王幸温阳之椒泉。以此本贮之 行宫。仍赐本郡之校。其后四十五年。即弘治元年也。忠清观察使金砺石与槐山郡守柳文通刊行之。凡二十三卷。清州教授金孝贞为序始末。其卷尾又题砺石,文通,孝贞及清州牧使金叙演,都事韩㬢,判官蔡允信,文义县令张汉弼,阴城县监孙元老。意其捐俸而锓梓者也。拓本既久。纸皆坏烂。想其板本又朽尽矣。余为改装。以备朝夕之观。噫此虽败蠹之馀。有以见 圣祖教士之意。与夫当时监司守宰所以对扬者。余又考阴城县监录名案。无孙元老。其他诸人亦俱未有著显于世。然考其存心经训则又不可泯灭。故历叙之。以备掌故。余闻北方少书籍。至若性理之诀。尤难得者。适茂山南积城阳进见过。闻其子弟多向学者。故举而遗之。庶有以发其学。余闻六镇之风。崇礼让敦孝悌。盖李松庵之教云。贤者之化如是夫。孰能继而开发如松庵者哉。然豪杰之士。岂有待而兴乎。北方之学者。其劝之哉。
余在阴城县购此书。乃考亭门人熊节编集宋朝濂洛诸贤所著述者也。 世宗庄宪大王幸温阳之椒泉。以此本贮之 行宫。仍赐本郡之校。其后四十五年。即弘治元年也。忠清观察使金砺石与槐山郡守柳文通刊行之。凡二十三卷。清州教授金孝贞为序始末。其卷尾又题砺石,文通,孝贞及清州牧使金叙演,都事韩㬢,判官蔡允信,文义县令张汉弼,阴城县监孙元老。意其捐俸而锓梓者也。拓本既久。纸皆坏烂。想其板本又朽尽矣。余为改装。以备朝夕之观。噫此虽败蠹之馀。有以见 圣祖教士之意。与夫当时监司守宰所以对扬者。余又考阴城县监录名案。无孙元老。其他诸人亦俱未有著显于世。然考其存心经训则又不可泯灭。故历叙之。以备掌故。余闻北方少书籍。至若性理之诀。尤难得者。适茂山南积城阳进见过。闻其子弟多向学者。故举而遗之。庶有以发其学。余闻六镇之风。崇礼让敦孝悌。盖李松庵之教云。贤者之化如是夫。孰能继而开发如松庵者哉。然豪杰之士。岂有待而兴乎。北方之学者。其劝之哉。题奋忠纾难录后
万历癸巳。倭将清正退屯蔚山西生浦。 皇朝总兵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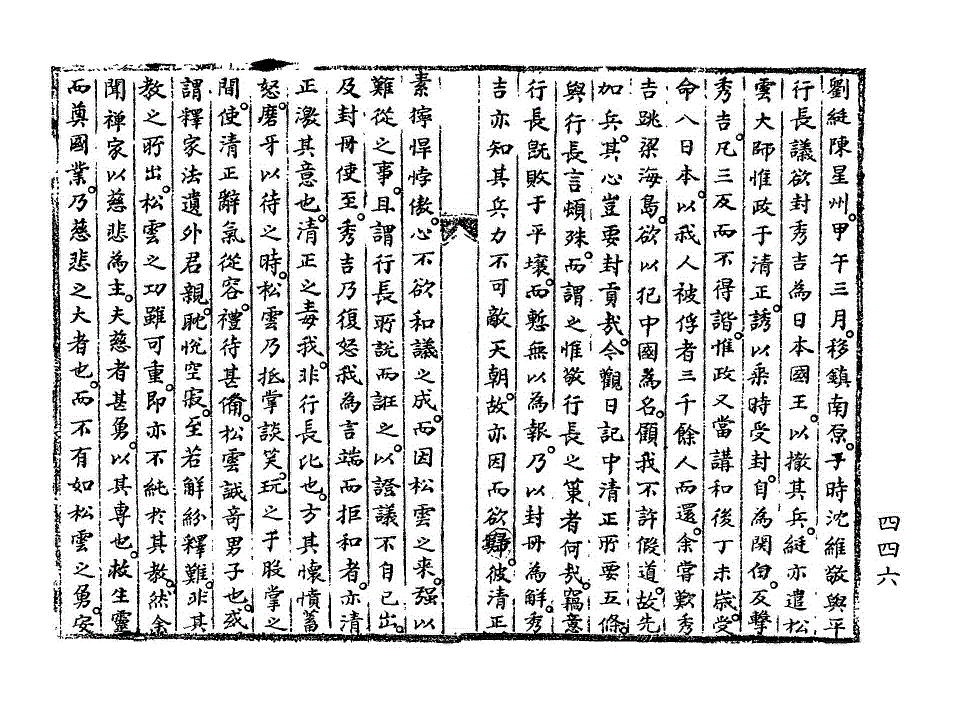 刘綎陈星州。甲午三月。移镇南原。于时沈维敬与平行长议欲封秀吉为日本国王。以撤其兵。綎亦遣松云大师惟政于清正。诱以乘时受封。自为关白。反击秀吉。凡三反而不得谐。惟政又当讲和后丁未岁。受命入日本。以我人被俘者三千馀人而还。余尝叹秀吉跳梁海岛。欲以犯中国为名。顾我不许假道。故先加兵。其心岂要封贡哉。今观日记中清正所要五条。与行长言顿殊。而谓之惟敬行长之策者何哉。窃意行长既败于平壤。而惭无以为报。乃以封册为解。秀吉亦知其兵力不可敌天朝。故亦因而欲归。彼清正素狞悍悖傲。心不欲和议之成。而因松云之来。强以难从之事。且谓行长所说而诳之。以證议不自己出。及封册使至。秀吉乃复怒我为言端而拒和者。亦清正激其意也。清正之毒我。非行长比也。方其怀愤蓄怒。磨牙以待之时。松云乃抵掌谈笑。玩之于股掌之间。使清正辞气从容。礼待甚备。松云诚奇男子也。或谓释家法遗外君亲。耽悦空寂。至若解纷释难。非其教之所出。松云之功虽可重。即亦不纯于其教。然余闻禅家以慈悲为主。夫慈者甚勇。以其专也。救生灵而奠国业。乃慈悲之大者也。而不有如松云之勇。安
刘綎陈星州。甲午三月。移镇南原。于时沈维敬与平行长议欲封秀吉为日本国王。以撤其兵。綎亦遣松云大师惟政于清正。诱以乘时受封。自为关白。反击秀吉。凡三反而不得谐。惟政又当讲和后丁未岁。受命入日本。以我人被俘者三千馀人而还。余尝叹秀吉跳梁海岛。欲以犯中国为名。顾我不许假道。故先加兵。其心岂要封贡哉。今观日记中清正所要五条。与行长言顿殊。而谓之惟敬行长之策者何哉。窃意行长既败于平壤。而惭无以为报。乃以封册为解。秀吉亦知其兵力不可敌天朝。故亦因而欲归。彼清正素狞悍悖傲。心不欲和议之成。而因松云之来。强以难从之事。且谓行长所说而诳之。以證议不自己出。及封册使至。秀吉乃复怒我为言端而拒和者。亦清正激其意也。清正之毒我。非行长比也。方其怀愤蓄怒。磨牙以待之时。松云乃抵掌谈笑。玩之于股掌之间。使清正辞气从容。礼待甚备。松云诚奇男子也。或谓释家法遗外君亲。耽悦空寂。至若解纷释难。非其教之所出。松云之功虽可重。即亦不纯于其教。然余闻禅家以慈悲为主。夫慈者甚勇。以其专也。救生灵而奠国业。乃慈悲之大者也。而不有如松云之勇。安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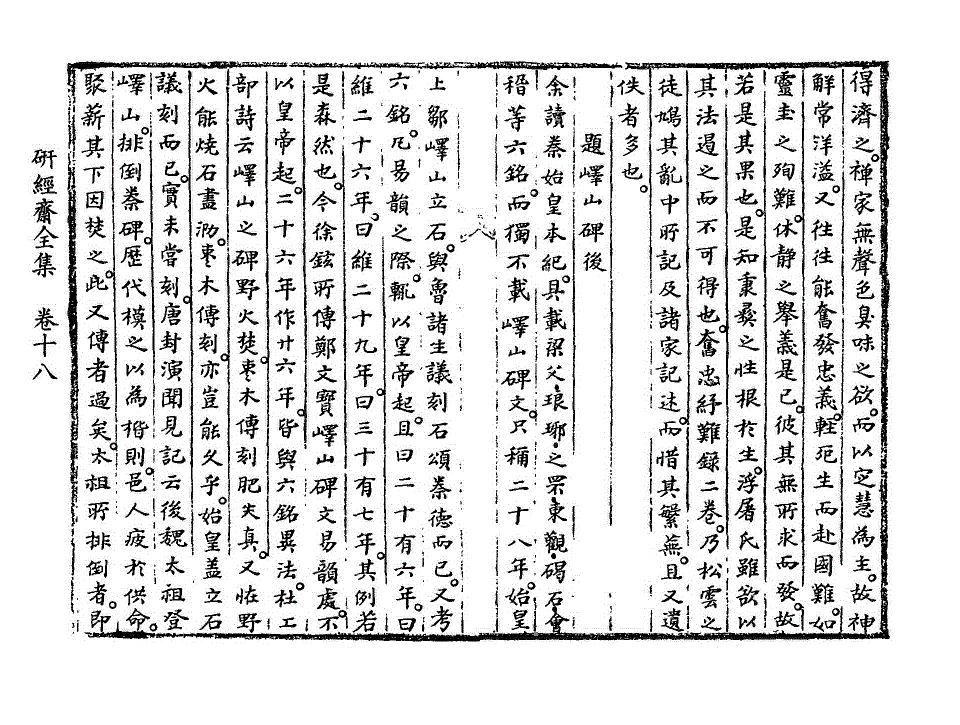 得济之。禅家无声色臭味之欲。而以定慧为主。故神解常洋溢。又往往能奋发忠义。轻死生而赴国难。如灵圭之殉难。休静之举义是已。彼其无所求而发。故若是其果也。是知秉彝之性根于生。浮屠氏虽欲以其法遏之而不可得也。奋忠纾难录二卷。乃松云之徒鸠其乱中所记及诸家记述。而惜其繁芜。且又遗佚者多也。
得济之。禅家无声色臭味之欲。而以定慧为主。故神解常洋溢。又往往能奋发忠义。轻死生而赴国难。如灵圭之殉难。休静之举义是已。彼其无所求而发。故若是其果也。是知秉彝之性根于生。浮屠氏虽欲以其法遏之而不可得也。奋忠纾难录二卷。乃松云之徒鸠其乱中所记及诸家记述。而惜其繁芜。且又遗佚者多也。题峄山碑后
余读秦始皇本纪。具载梁父,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六铭。而独不载峄山碑文。只称二十八年。始皇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而已。又考六铭。凡易韵之际。辄以皇帝起。且曰二十有六年。曰维二十六年。曰维二十九年。曰三十有七年。其例若是森然也。今徐铉所传郑文宝峄山碑文易韵处。不以皇帝起。二十六年作廿六年。皆与六铭异法。杜工部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又怪野火能烧石尽泐。枣木传刻。亦岂能久乎。始皇盖立石议刻而已。实未尝刻。唐封演闻见记云后魏太祖登峄山。排倒秦碑。历代模之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焚之。此又传者过矣。太祖所排倒者。即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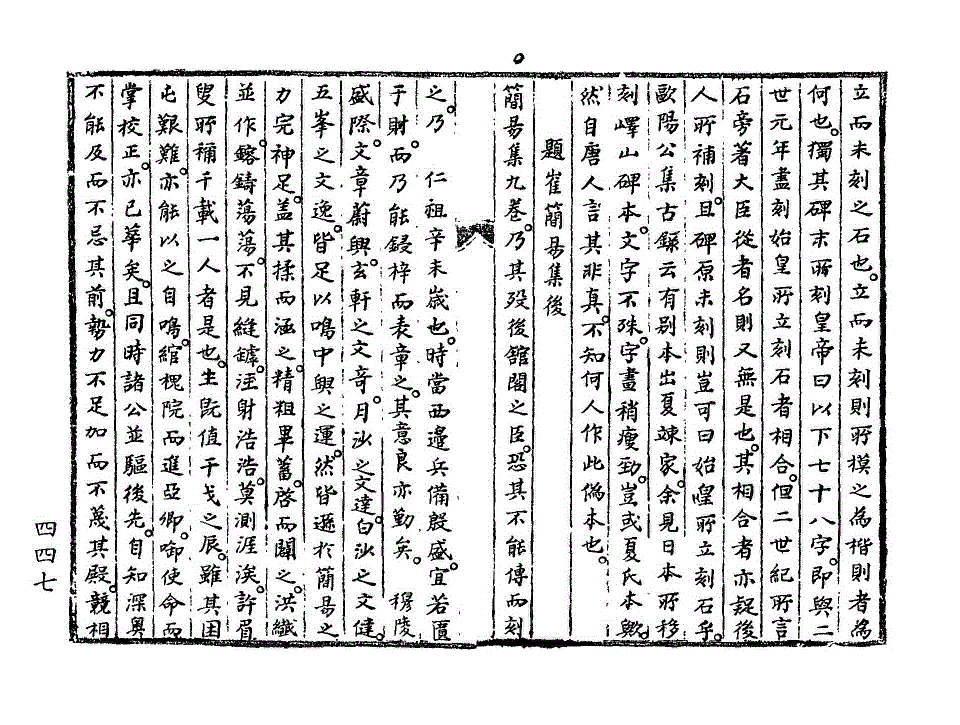 立而未刻之石也。立而未刻则所模之为楷则者为何也。独其碑末所刻皇帝曰以下七十八字。即与二世元年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者相合。但二世纪所言石旁著大臣从者名则又无是也。其相合者亦疑后人所补刻。且碑原未刻则岂可曰始皇所立刻石乎。欧阳公集古录云有别本出夏竦家。余见日本所移刻峄山碑本。文字不殊。字画稍瘦劲。岂或夏氏本欤。然自唐人言其非真。不知何人作此伪本也。
立而未刻之石也。立而未刻则所模之为楷则者为何也。独其碑末所刻皇帝曰以下七十八字。即与二世元年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者相合。但二世纪所言石旁著大臣从者名则又无是也。其相合者亦疑后人所补刻。且碑原未刻则岂可曰始皇所立刻石乎。欧阳公集古录云有别本出夏竦家。余见日本所移刻峄山碑本。文字不殊。字画稍瘦劲。岂或夏氏本欤。然自唐人言其非真。不知何人作此伪本也。题崔简易集后
简易集九卷。乃其殁后馆阁之臣。恐其不能传而刻之。乃 仁祖辛未岁也。时当西边兵备殷盛。宜若匮于财。而乃能锓梓而表章之。其意良亦勤矣。 穆陵盛际。文章蔚兴。玄轩之文奇。月沙之文达。白沙之文健。五峰之文逸。皆足以鸣中兴之运。然皆逊于简易之力完神足。盖其揉而涵之。精粗毕蓄。启而辟之。洪纤并作。镕铸荡荡。不见缝罅。注射浩浩。莫测涯涘。许眉叟所称千载一人者是也。生既值干戈之辰。虽其困屯艰难。亦能以之自鸣。绾槐院而进亚卿。衔使命而掌校正。亦已华矣。且同时诸公并驱后先。自知深奥不能及而不忌其前。势力不足加而不蔑其殿。竞相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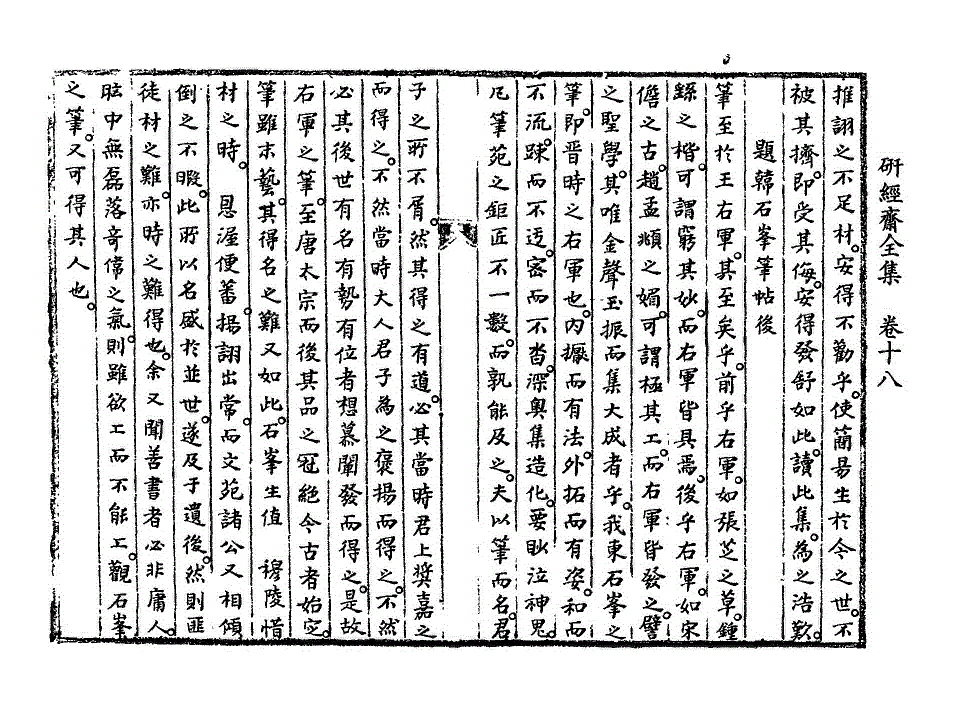 推诩之不足材。安得不劝乎。使简易生于今之世。不被其挤。即受其侮。安得发舒如此。读此集。为之浩叹。
推诩之不足材。安得不劝乎。使简易生于今之世。不被其挤。即受其侮。安得发舒如此。读此集。为之浩叹。题韩石峰笔帖后
笔至于王右军。其至矣乎。前乎右军。如张芝之草。钟繇之楷。可谓穷其妙。而右军皆具焉。后乎右军。如宋儋之古。赵孟頫之媚。可谓极其工。而右军皆发之。譬之圣学。其唯金声玉振而集大成者乎。我东石峰之笔。即晋时之右军也。内擪而有法。外拓而有姿。和而不流。疏而不迂。密而不沓。深奥集造化。要眇泣神鬼。凡笔苑之钜匠不一数。而孰能及之。夫以笔而名。君子之所不屑。然其得之有道。必其当时君上奖嘉之而得之。不然当时大人君子为之褒扬而得之。不然必其后世有名有势有位者想慕阐发而得之。是故右军之笔。至唐太宗而后其品之冠绝今古者始定。笔虽末艺。其得名之难又如此。石峰生值 穆陵惜材之时。 恩渥便蕃。扬诩出常。而文苑诸公又相倾倒之不暇。此所以名盛于并世。遂及于遗后。然则匪徒材之难。亦时之难得也。余又闻善书者必非庸人。胸中无磊落奇伟之气。则虽欲工而不能工。观石峰之笔。又可得其人也。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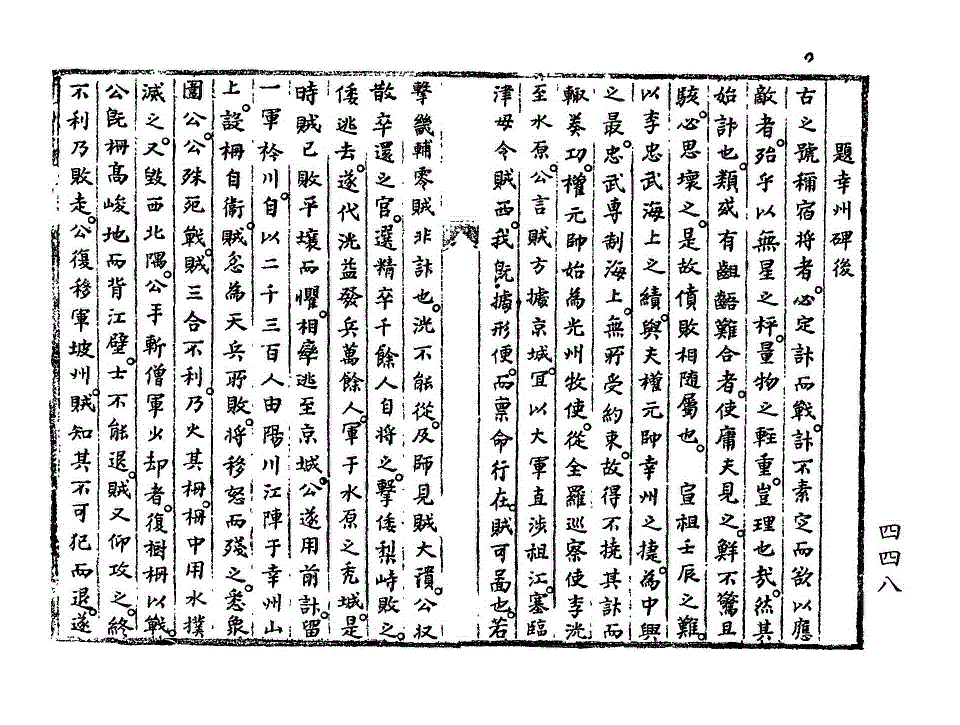 题幸州碑后
题幸州碑后古之号称宿将者。必定计而战。计不素定而欲以应敌者。殆乎以无星之枰。量物之轻重。岂理也哉。然其始计也。类或有龃龉难合者。使庸夫见之。鲜不惊且骇。必思坏之。是故偾败相随属也。 宣祖壬辰之难。以李忠武海上之绩。与夫权元帅幸州之捷。为中兴之最。忠武专制海上。无所受约束。故得不挠其计而辄奏功。权元帅始为光州牧使。从全罗巡察使李洸至水原。公言贼方据京城。宜以大军直涉祖江。塞临津毋令贼西。我既据形便。而禀命行在。贼可啚也。若击畿辅零贼非计也。洸不能从。及师见贼大溃。公收散卒还之官。选精卒千馀人自将之。击倭梨峙败之。倭逃去。遂代洸益发兵万馀人。军于水原之秃城。是时贼已败平壤而惧。相率逃至京城。公遂用前计。留一军衿川。自以二千三百人由阳川江阵于幸州山上。设栅自卫。贼忿为天兵所败。将移怒而残之。悉众围公。公殊死战。贼三合不利。乃火其栅。栅中用水扑灭之。又毁西北隅。公手斩僧军少却者。复树栅以战。公既栅高峻地而背江壁。士不能退。贼又仰攻之。终不利乃败走。公复移军坡州。贼知其不可犯而退。遂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9H 页
 复京城。此公所以素定计也。是故局于拘掣则偾。专于节制则济。向使李提督不以少衄而回。沈维敬不以和议而误。倭宁渠得一人返哉。夫倭寇狡诈闪忽。方其战也。趍利忘死。及其败也。奔崩如遗。其自釜山而西上也。列镇自坏。虽其接刃而斗。如李镒之尚州。申砬之忠州。特儿戏耳。自我先丧而谓倭之善战可乎。天兵一振于平壤而震惧惊慑之不暇。盖倭之轻锐虽难敌。其实易挠也。使当时诸将极兵威而力斗。不必假天兵之武而可即破也。是故李忠武兵未必皆练而倭辄糜碎。权元帅师甚寡弱而倭亦摧破。盖其定计。在据险而力战也。余尝考归震川备倭议。以为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用是而究倭情则尽然矣。盖上岸则已死地。啚生于必死。所以难敌也。然则忠武之绩。当倭在海也。权公之绩。在上岸矣。其劳绩之难易。又可知矣。今观崔简易幸州碑云公丁酉冬。从麻提督蔚山之役。戊戌秋。从刘提督顺天之役。皆以体统有制。有先见之言而不用。有先登之勇而不效。不独公自抆英泪。志士共惜之。此深得当时机务之失。为之慨然太息也。
复京城。此公所以素定计也。是故局于拘掣则偾。专于节制则济。向使李提督不以少衄而回。沈维敬不以和议而误。倭宁渠得一人返哉。夫倭寇狡诈闪忽。方其战也。趍利忘死。及其败也。奔崩如遗。其自釜山而西上也。列镇自坏。虽其接刃而斗。如李镒之尚州。申砬之忠州。特儿戏耳。自我先丧而谓倭之善战可乎。天兵一振于平壤而震惧惊慑之不暇。盖倭之轻锐虽难敌。其实易挠也。使当时诸将极兵威而力斗。不必假天兵之武而可即破也。是故李忠武兵未必皆练而倭辄糜碎。权元帅师甚寡弱而倭亦摧破。盖其定计。在据险而力战也。余尝考归震川备倭议。以为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用是而究倭情则尽然矣。盖上岸则已死地。啚生于必死。所以难敌也。然则忠武之绩。当倭在海也。权公之绩。在上岸矣。其劳绩之难易。又可知矣。今观崔简易幸州碑云公丁酉冬。从麻提督蔚山之役。戊戌秋。从刘提督顺天之役。皆以体统有制。有先见之言而不用。有先登之勇而不效。不独公自抆英泪。志士共惜之。此深得当时机务之失。为之慨然太息也。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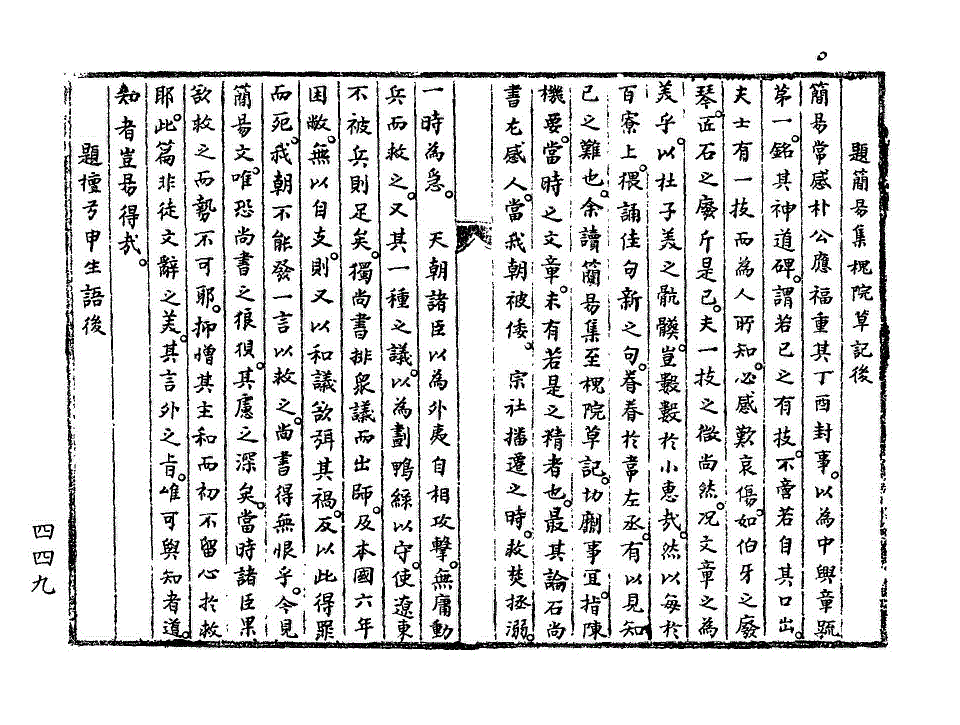 题简易集槐院草记后
题简易集槐院草记后简易常感朴公应福重其丁酉封事。以为中兴章疏第一。铭其神道碑。谓若己之有技。不啻若自其口出。夫士有一技而为人所知。必感叹哀伤。如伯牙之废琴。匠石之废斤是已。夫一技之微尚然。况文章之为美乎。以杜子美之肮脏。岂数数于小惠哉。然以每于百寮上。猥诵佳句新之句。眷眷于韦左丞。有以见知己之难也。余读简易集至槐院草记。切劘事宜。指陈机要。当时之文章。未有若是之精者也。最其论石尚书尤感人。当我朝被倭。 宗社播迁之时。救焚拯溺。一时为急。 天朝诸臣以为外夷自相攻击。无庸动兵而救之。又其一种之议。以为划鸭绿以守。使辽东不被兵则足矣。独尚书排众议而出师。及本国六年困敝。无以自支。则又以和议欲弭其祸。反以此得罪而死。我朝不能发一言以救之。尚书得无恨乎。今见简易文。唯恐尚书之狼狈。其虑之深矣。当时诸臣果欲救之而势不可耶。抑憎其主和而初不留心于救耶。此篇非徒文辞之美。其言外之旨。唯可与知者道。知者岂易得哉。
题檀弓申生语后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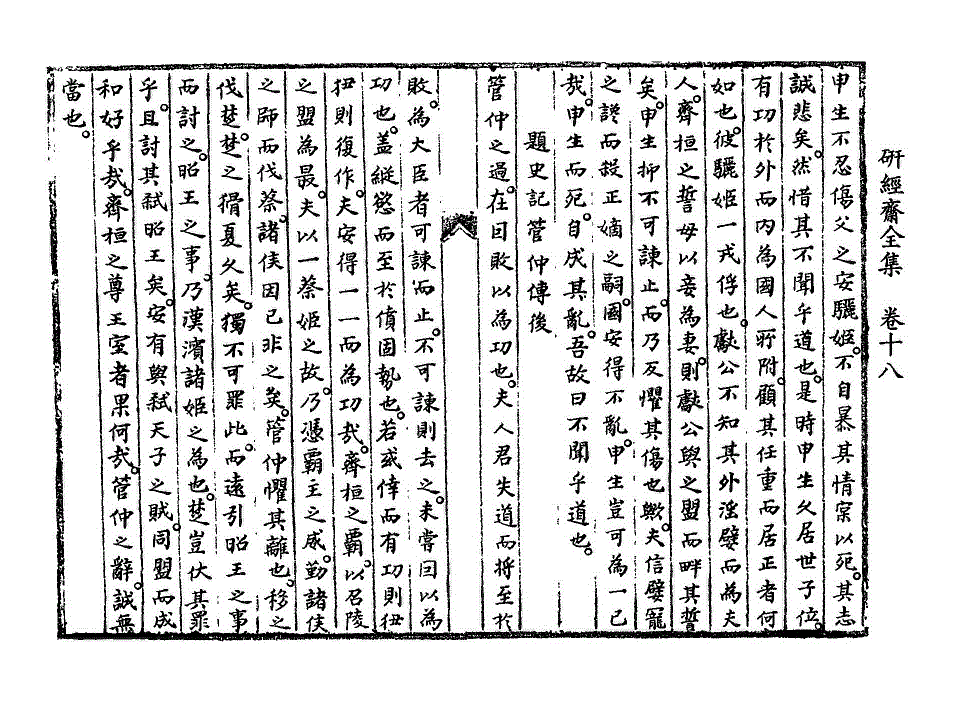 申生不忍伤父之安骊姬。不自暴其情宲以死。其志诚悲矣。然惜其不闻乎道也。是时申生久居世子位。有功于外而内为国人所附。顾其任重而居正者何如也。彼骊姬一戎俘也。献公不知其外淫嬖而为夫人。齐桓之誓毋以妾为妻。则献公与之盟而畔其誓矣。申生抑不可谏止。而乃反惧其伤也欤。夫信嬖宠之谗而杀正嫡之嗣。国安得不乱。申生岂可为一己哉。申生而死。自成其乱。吾故曰不闻乎道也。
申生不忍伤父之安骊姬。不自暴其情宲以死。其志诚悲矣。然惜其不闻乎道也。是时申生久居世子位。有功于外而内为国人所附。顾其任重而居正者何如也。彼骊姬一戎俘也。献公不知其外淫嬖而为夫人。齐桓之誓毋以妾为妻。则献公与之盟而畔其誓矣。申生抑不可谏止。而乃反惧其伤也欤。夫信嬖宠之谗而杀正嫡之嗣。国安得不乱。申生岂可为一己哉。申生而死。自成其乱。吾故曰不闻乎道也。题史记管仲传后
管仲之过。在因败以为功也。夫人君失道而将至于败。为大臣者可谏而止。不可谏则去之。未尝因以为功也。盖纵欲而至于偾固势也。若或倖而有功则狃狃则复作。夫安得一一而为功哉。齐桓之霸。以召陵之盟为最。夫以一蔡姬之故。乃凭霸主之威。勤诸侯之师而伐蔡。诸侯因已非之矣。管仲惧其离也。移之伐楚。楚之猾夏久矣。独不可罪此。而远引昭王之事而讨之。昭王之事。乃汉滨诸姬之为也。楚岂伏其罪乎。且讨其弑昭王矣。安有与弑天子之贼。同盟而成和好乎哉。齐桓之尊王室者果何哉。管仲之辞。诚无当也。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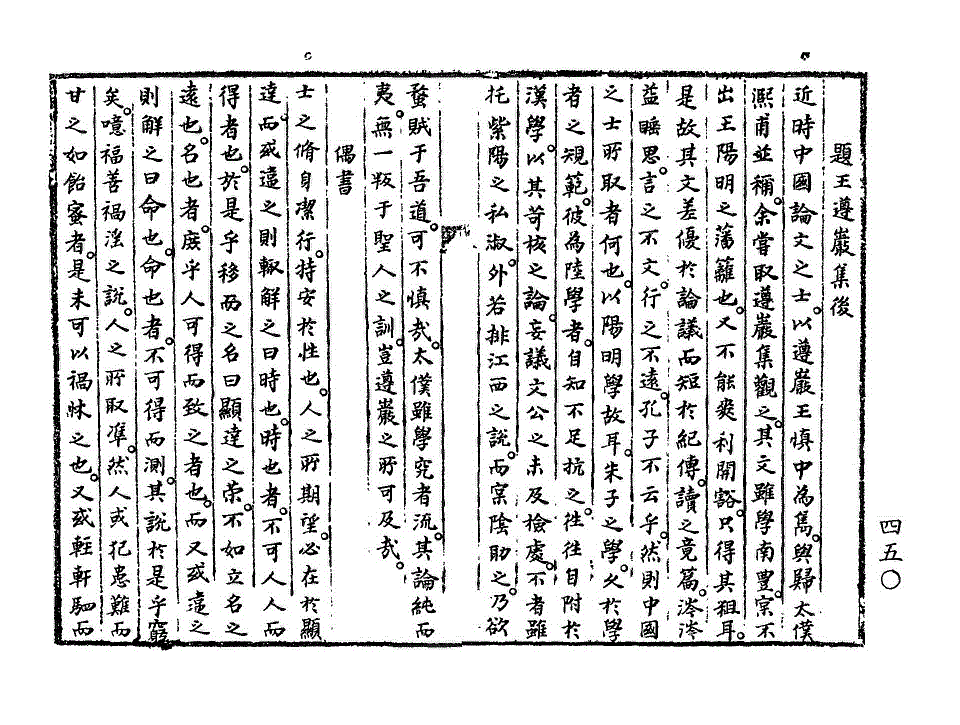 题王遵岩集后
题王遵岩集后近时中国论文之士。以遵岩王慎中为隽。与归太仆熙甫并称。余尝取遵岩集观之。其文虽学南礼。宲不出王阳明之藩篱也。又不能爽利开豁。只得其粗耳。是故其文差优于论议而短于纪传。读之竟篇。涔涔益睡思。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孔子不云乎。然则中国之士所取者何也。以阳明学故耳。朱子之学。久于学者之规范。彼为陆学者。自知不足抗之。往往自附于汉学。以其苛核之论。妄议文公之未及检处。不者虽托紫阳之私淑。外若排江西之说。而宲阴助之。乃欲蝥贼于吾道。可不慎哉。太仆虽学究者流。其论纯而夷。无一叛于圣人之训。岂遵岩之所可及哉。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文二○杂著
偶书
士之脩身洁行。特安于性也。人之所期望。必在于显达。而或违之则辄解之曰时也。时也者。不可人人而得者也。于是乎移之名曰。显达之荣。不如立名之远也。名也者。庶乎人可得而致之者也。而又或违之则解之曰命也。命也者。不可得而测。其说于是乎穷矣。噫福善祸淫之说。人之所取准。然人或犯患难而甘之如饴蜜者。是未可以祸怵之也。又或轻轩驷而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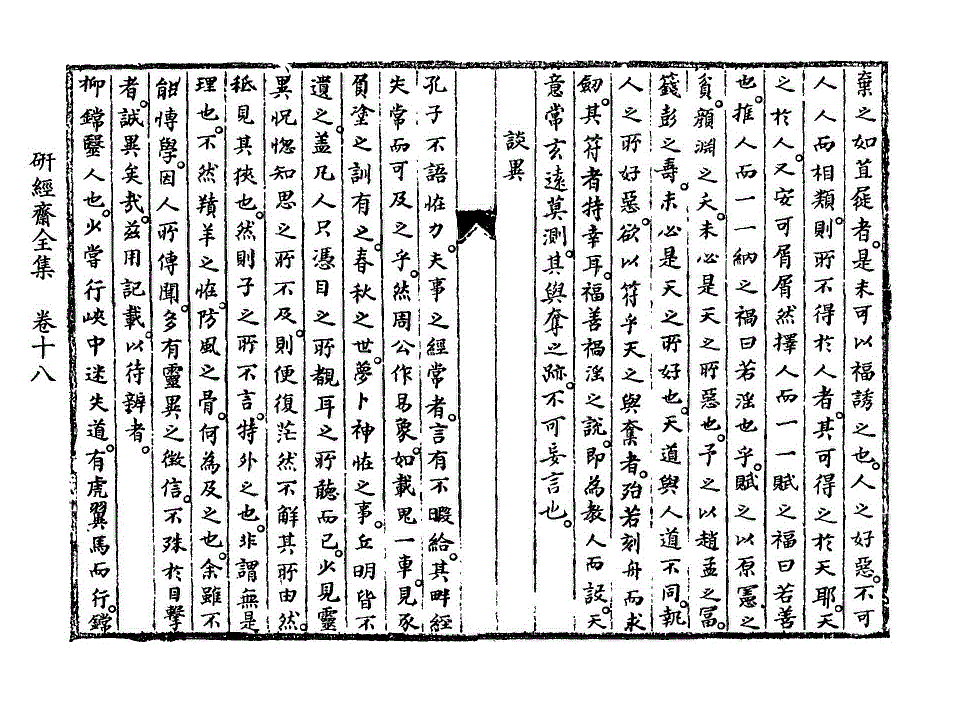 弃之如苴屣者。是未可以福诱之也。人之好恶。不可人人而相类。则所不得于人者。其可得之于天耶。天之于人。又安可屑屑然择人而一一赋之福曰若善也。推人而一一纳之祸曰若淫也乎。赋之以原宪之贫。颜渊之夭。未必是天之所恶也。予之以赵孟之富。篯彭之寿。未必是天之所好也。天道与人道不同。执人之所好恶。欲以符乎天之与夺者。殆若刻舟而求剑。其符者特幸耳。福善祸淫之说。即为教人而设。天意常玄远莫测。其与夺之迹。不可妄言也。
弃之如苴屣者。是未可以福诱之也。人之好恶。不可人人而相类。则所不得于人者。其可得之于天耶。天之于人。又安可屑屑然择人而一一赋之福曰若善也。推人而一一纳之祸曰若淫也乎。赋之以原宪之贫。颜渊之夭。未必是天之所恶也。予之以赵孟之富。篯彭之寿。未必是天之所好也。天道与人道不同。执人之所好恶。欲以符乎天之与夺者。殆若刻舟而求剑。其符者特幸耳。福善祸淫之说。即为教人而设。天意常玄远莫测。其与夺之迹。不可妄言也。谈异
孔子不语怪力。夫事之经常者。言有不暇给。其畔经失常而可及之乎。然周公作易象。如载鬼一车。见豕负涂之训有之。春秋之世。梦卜神怪之事。丘明皆不遗之。盖凡人只凭目之所睹耳之所听而已。少见灵异恍惚知思之所不及。则便复茫然不解其所由然。秪见其狭也。然则子之所不言。特外之也。非谓无是理也。不然羵羊之怪。防风之骨。何为及之也。余虽不能博学。因人所传闻。多有灵异之徵信。不殊于目击者。诚异矣哉。玆用记载。以待辨者。
柳鋿医人也。少尝行峡中迷失道。有虎翼马而行。鋿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1L 页
 惧不敢下。第任之。至最奥处。日暮虎去。见茅屋甚洁。童子开户视曰客至矣。主人迎之。须眉皓白甚慇勤。少顷有二老人至。主人谓鋿少待。吾辈有事出他。寻当还矣。遂相率而出。鋿见案上多书帙。抽观之。字皆不可辨。夜将半。三人至。带血腥狼籍。鋿问往何所。答云湖西之某地。有水贼要国家税米船。将取之。吾三人往诛之。天将晓。鋿欲还。主人与一书曰善读之。后当有用此时。鋿受视之。乃治痘方也。后鋿以医进。当肃庙患痘时。卒获其用。书中术多世所不传者。
惧不敢下。第任之。至最奥处。日暮虎去。见茅屋甚洁。童子开户视曰客至矣。主人迎之。须眉皓白甚慇勤。少顷有二老人至。主人谓鋿少待。吾辈有事出他。寻当还矣。遂相率而出。鋿见案上多书帙。抽观之。字皆不可辨。夜将半。三人至。带血腥狼籍。鋿问往何所。答云湖西之某地。有水贼要国家税米船。将取之。吾三人往诛之。天将晓。鋿欲还。主人与一书曰善读之。后当有用此时。鋿受视之。乃治痘方也。后鋿以医进。当肃庙患痘时。卒获其用。书中术多世所不传者。李廷楷完山人。少居广州。娶妻而美耽之。妻曰以吾之故。君困矣。若复来就我。我将死。廷楷曰诺。未几又就之。妻曰吾与君约死。而君不之顾。吾死矣。即自缢死。廷楷恨其以己而致之死。何以养为。遂弃田宅仆隶。游于四方。畏人识之。自称李平凉子。从所戴而称之也。常偶言纵我如此。渠岂复然乎哉。盖恨妻之辞也。先君子尝家宣仁门外。烧肉为会。廷楷闻而至。食之甚馋。叶下权公曰其食饮非常性也。余亦不甚异之。后死于坡州之店舍。今因尹奉化东寿闻。廷楷往麻田一姻家。求饮酱。其家知素善饮。出数盆即吸之尽。其没后门徒适往鸟岭。一白鹿在路傍。廷楷倚石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2H 页
 上而睡。门徒惊曰谓公死矣。公乃不死耶。廷楷起曰若何从至也。仍骑鹿去。不知所之。此尹老所的闻也。岂世所称神仙者多混迹凡庸。故人多不能知也欤。士固不可轻论哉。
上而睡。门徒惊曰谓公死矣。公乃不死耶。廷楷起曰若何从至也。仍骑鹿去。不知所之。此尹老所的闻也。岂世所称神仙者多混迹凡庸。故人多不能知也欤。士固不可轻论哉。许珩阳川人。徙抱川。年二十。尝梦为鬼所摄。至天帝前。殿宇崇严。冠佩璀璨。帝谓珩曰吾欲使汝为侍人。汝妻为侍女。珩仰见其妻亦在帝傍。即具言早失父。独与祖父及母居。不可舍之而侍帝。乞赦之。帝复捡一册曰若先期至。若年四十八岁。即复来。珩叩谢而退。自卜吾寿虽促。既尝侍上帝。此登科之兆也。时 正宗大王幸 光陵。试杨抱二邑之士。珩匿家人。潜从善赋者赴场屋。预嘱妻具酒以待榜。榜出果登壮元。珩尝以是语权稚琴。珩策名两司。出知慈仁县。为人孝于亲。及至四十八岁。其母有疾甚剧。昼夜救药。母疾已而珩病。稚琴曰其将践梦乎。珩果卒。
姜百能江华人。以武举官至通津府使。老为府千揔。叶下权公甲寅中。留守江华。稚琴往待衙内。百能尝从容言某尝为草溪郡守。将赴任。八月十六日至水原。阻水不得发。店舍无聊。因店人知邻居黄生某可与谈。即遣隶请至。即至谈移时。日将暮辞去。挽之不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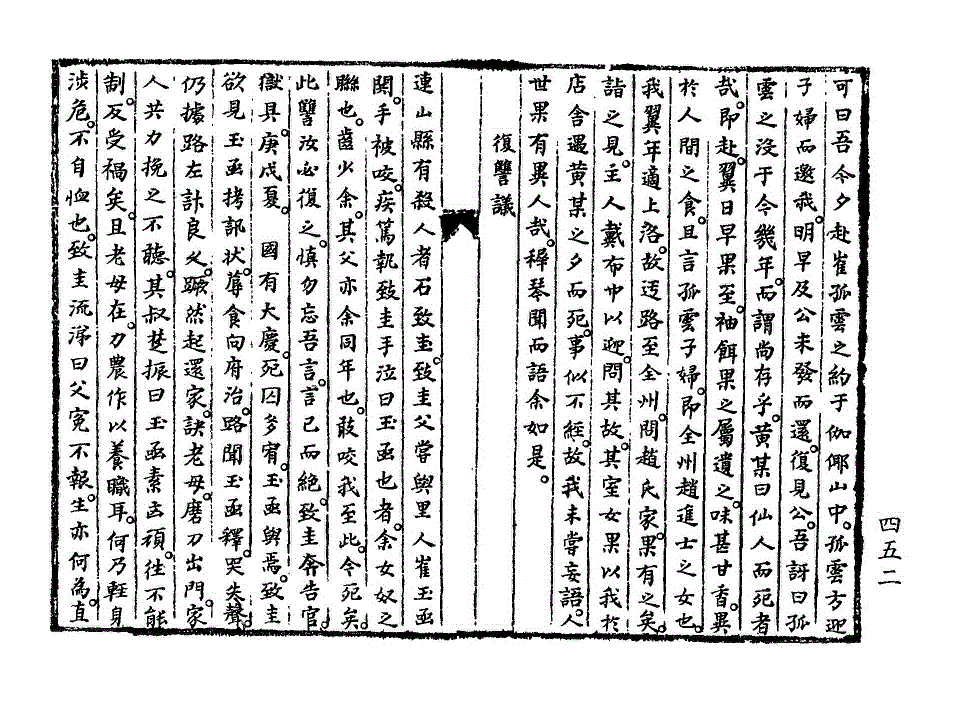 可曰吾今夕赴崔孤云之约于伽倻山中。孤云方迎子妇而邀我。明早及公未发而还。复见公。吾讶曰孤云之没于今几年。而谓尚存乎。黄某曰仙人而死者哉。即赴。翼日早果至。袖饵果之属遗之。味甚甘香。异于人间之食。且言孤云子妇。即全州赵进士之女也。我翼年适上洛。故迂路至全州。问赵氏家。果有之矣。诣之见。主人戴布巾以迎。问其故。其室女果以我于店舍遇黄某之夕而死。事似不经。故我未尝妄语。人世果有异人哉。稚琴闻而语余如是。
可曰吾今夕赴崔孤云之约于伽倻山中。孤云方迎子妇而邀我。明早及公未发而还。复见公。吾讶曰孤云之没于今几年。而谓尚存乎。黄某曰仙人而死者哉。即赴。翼日早果至。袖饵果之属遗之。味甚甘香。异于人间之食。且言孤云子妇。即全州赵进士之女也。我翼年适上洛。故迂路至全州。问赵氏家。果有之矣。诣之见。主人戴布巾以迎。问其故。其室女果以我于店舍遇黄某之夕而死。事似不经。故我未尝妄语。人世果有异人哉。稚琴闻而语余如是。复雠议
连山县有杀人者石致圭。致圭父尝与里人崔玉函閧。手被咬。疾笃执致圭手泣曰玉函也者。余女奴之联也。齿少余。其父亦余同年也。敢咬我至此。今死矣。此雠汝必复之。慎勿忘吾言。言已而绝。致圭奔告官。狱具。庚戌夏。 国有大庆。死囚多宥。玉函与焉。致圭欲见玉函拷讯状。蓐食向府治。路闻玉函释。哭失声。仍据路左计良久。蹶然起还家。诀老母。磨刀出门。家人共力挽之不听。其叔楚振曰玉函素凶顽。往不能制。反受祸矣。且老母在。力农作以养职耳。何乃轻身涉危。不自恤也。致圭流涕曰父冤不报。生亦何为。直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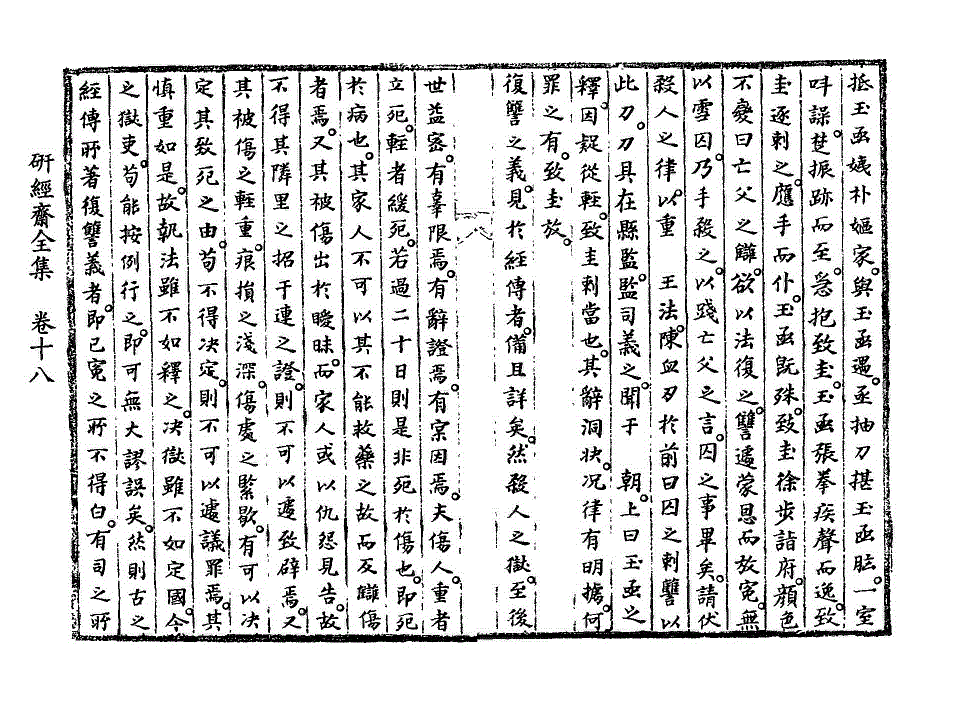 抵玉函姨朴妪家。与玉函遇。亟抽刀揕玉函胸。一室叫噪。楚振迹而至。急抱致圭。玉函张拳疾声而逸。致圭逐刺之。应手而仆。玉函既殊。致圭徐步诣府。颜色不变曰亡父之雠。欲以法复之。雠遽蒙恩而放冤。无以雪囚。乃手杀之。以践亡父之言。囚之事毕矣。请伏杀人之律。以重 王法。陈血刃于前曰囚之刺雠以此刀。刀具在县监。监司义之。闻于 朝。上曰玉函之释。因疑从轻。致圭刺当也。其辞洞快。况律有明据。何罪之有。致圭放。
抵玉函姨朴妪家。与玉函遇。亟抽刀揕玉函胸。一室叫噪。楚振迹而至。急抱致圭。玉函张拳疾声而逸。致圭逐刺之。应手而仆。玉函既殊。致圭徐步诣府。颜色不变曰亡父之雠。欲以法复之。雠遽蒙恩而放冤。无以雪囚。乃手杀之。以践亡父之言。囚之事毕矣。请伏杀人之律。以重 王法。陈血刃于前曰囚之刺雠以此刀。刀具在县监。监司义之。闻于 朝。上曰玉函之释。因疑从轻。致圭刺当也。其辞洞快。况律有明据。何罪之有。致圭放。复雠之义。见于经传者。备且详矣。然杀人之狱。至后世益密。有辜限焉。有辞證焉。有宲因焉。夫伤人。重者立死。轻者缓死。若过二十日则是非死于伤也。即死于病也。其家人不可以其不能救药之故而反雠伤者焉。又其被伤出于瞹昧。而家人或以仇怨见告。故不得其邻里之招干连之證。则不可以遽致辟焉。又其被伤之轻重。痕损之浅深。伤处之紧歇。有可以决定其致死之由。苟不得决定。则不可以遽议罪焉。其慎重如是。故执法虽不如释之。决狱虽不如定国。今之狱吏。苟能按例行之。即可无大谬误矣。然则古之经传所著复雠义者。即己冤之所不得白。有司之所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3L 页
 不能听也。 正宗大王圣德宽仁。每审理重囚。日晏进膳。夜烛屡跋。究情而即乎疑。考迹而原乎义。死者无冤。生者无枉。夫玉函之释以疑。致圭之宥以义也。然此乃造化之权。非有司之所可援也。夫狱具而谳矣。谳而判矣。彼有可生之道。故傅之生矣。致圭乃以父死为玉函之咬而径杀之。有司之议而 王言之判也。而乃不顾焉。如是则法安所施哉。处心积虑。以冲雠人之胸者。如徐元庆梁悦而后可论已。若致圭者。真所谓亲亲相雠。其乱谁救者也。如使致圭必欲报雠。即当鸣冤于 朝。备陈辜限宲因痕损之由。一有可执而为言者。则有司当量其轻重而处之。苟于此三者而无疑焉。徒欲践其父之言而杀之者。于法果何如也。昌黎之文曰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然欲报雠者。虽孤稚羸弱。其所摩厉以待者。奋发雄壮。固可以敌丈夫。况如致圭之壮者哉。致圭即犯法。非复雠者也。吾恐执法者援以为常。故辨之如此。
不能听也。 正宗大王圣德宽仁。每审理重囚。日晏进膳。夜烛屡跋。究情而即乎疑。考迹而原乎义。死者无冤。生者无枉。夫玉函之释以疑。致圭之宥以义也。然此乃造化之权。非有司之所可援也。夫狱具而谳矣。谳而判矣。彼有可生之道。故傅之生矣。致圭乃以父死为玉函之咬而径杀之。有司之议而 王言之判也。而乃不顾焉。如是则法安所施哉。处心积虑。以冲雠人之胸者。如徐元庆梁悦而后可论已。若致圭者。真所谓亲亲相雠。其乱谁救者也。如使致圭必欲报雠。即当鸣冤于 朝。备陈辜限宲因痕损之由。一有可执而为言者。则有司当量其轻重而处之。苟于此三者而无疑焉。徒欲践其父之言而杀之者。于法果何如也。昌黎之文曰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然欲报雠者。虽孤稚羸弱。其所摩厉以待者。奋发雄壮。固可以敌丈夫。况如致圭之壮者哉。致圭即犯法。非复雠者也。吾恐执法者援以为常。故辨之如此。记旧奴婢事
吾家旧贫甚。先王考由安山之职串村。徙居抱川之
研经斋全集卷之十八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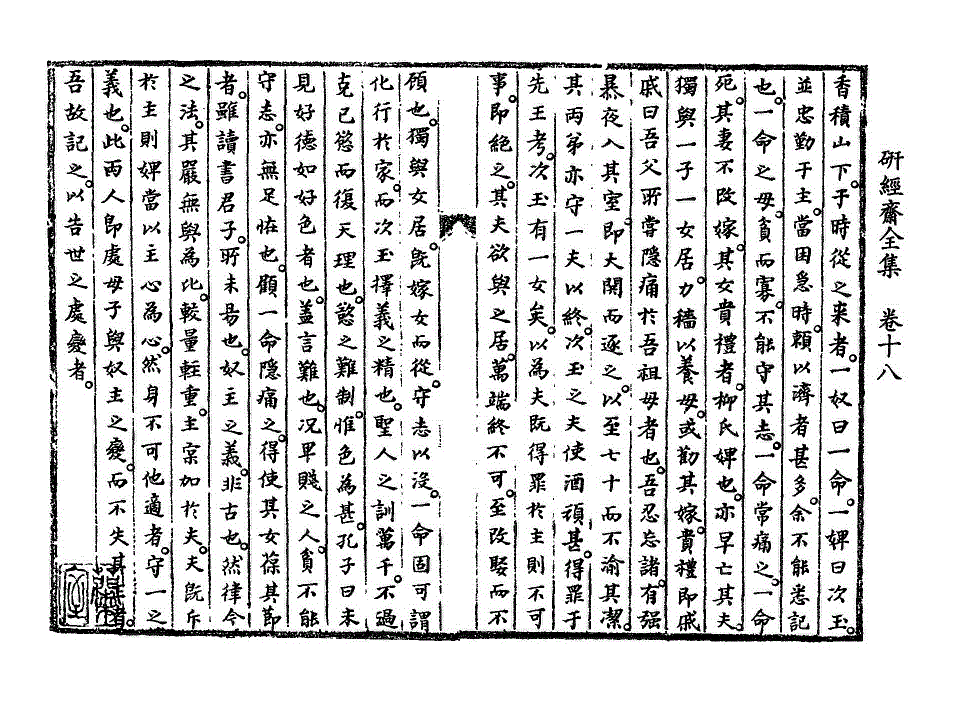 香积山下。于时从之来者。一奴曰一命。一婢曰次玉。并忠勤于主。当困急时。赖以济者甚多。余不能悉记也。一命之母。贫而寡。不能守其志。一命常痛之。一命死。其妻不改嫁。其女贵礼者。柳氏婢也。亦早亡其夫。独与一子一女居。力穑以养母。或劝其嫁。贵礼即戚戚曰吾父所尝隐痛于吾祖母者也。吾忍忘诸。有强暴夜入其室。即大閧而逐之。以至七十而不渝其洁。其两弟亦守一夫以终。次玉之夫使酒顽甚。得罪于先王考。次玉有一女矣。以为夫既得罪于主则不可事。即绝之。其夫欲与之居。万端终不可。至改娶而不顾也。独与女居。既嫁女而从。守志以没。一命固可谓化行于家。而次玉择义之精也。圣人之训万千。不过克己欲而复天理也。欲之难制。惟色为甚。孔子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盖言难也。况卑贱之人。贫不能守志。亦无足怪也。顾一命隐痛之。得使其女葆其节者。虽读书君子。所未易也。奴主之义。非古也。然律今之法。其严无与为比。较量轻重。主宲加于夫。夫既斥于主则婢当以主心为心。然身不可他适者。守一之义也。此两人即处母子与奴主之变。而不失其正者。吾故记之。以告世之处变者。
香积山下。于时从之来者。一奴曰一命。一婢曰次玉。并忠勤于主。当困急时。赖以济者甚多。余不能悉记也。一命之母。贫而寡。不能守其志。一命常痛之。一命死。其妻不改嫁。其女贵礼者。柳氏婢也。亦早亡其夫。独与一子一女居。力穑以养母。或劝其嫁。贵礼即戚戚曰吾父所尝隐痛于吾祖母者也。吾忍忘诸。有强暴夜入其室。即大閧而逐之。以至七十而不渝其洁。其两弟亦守一夫以终。次玉之夫使酒顽甚。得罪于先王考。次玉有一女矣。以为夫既得罪于主则不可事。即绝之。其夫欲与之居。万端终不可。至改娶而不顾也。独与女居。既嫁女而从。守志以没。一命固可谓化行于家。而次玉择义之精也。圣人之训万千。不过克己欲而复天理也。欲之难制。惟色为甚。孔子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盖言难也。况卑贱之人。贫不能守志。亦无足怪也。顾一命隐痛之。得使其女葆其节者。虽读书君子。所未易也。奴主之义。非古也。然律今之法。其严无与为比。较量轻重。主宲加于夫。夫既斥于主则婢当以主心为心。然身不可他适者。守一之义也。此两人即处母子与奴主之变。而不失其正者。吾故记之。以告世之处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