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惕斋集卷之十三
尚书讲义[四]
尚书讲义[四]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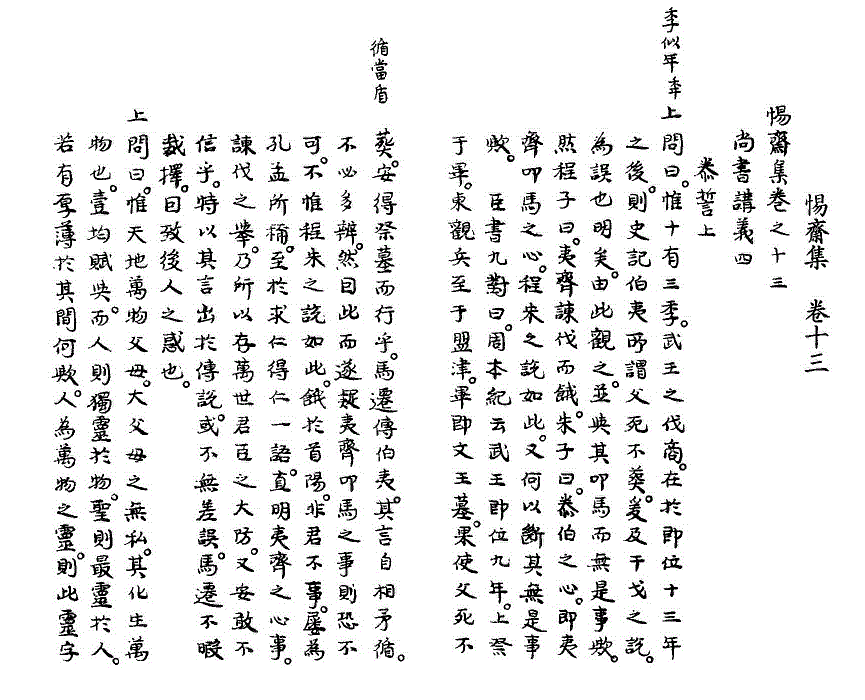 泰誓上
泰誓上上问曰。惟十有三季(季似年(䄵)
)。武王之伐商。在于即位十三年之后。则史记伯夷所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说。为误也明矣。由此观之。并与其叩马而无是事欤。然程子曰。夷齐谏伐而饿。朱子曰。泰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程朱之说如此。又何以断其无是事欤。
臣书九对曰。周本纪云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毕即文王墓。果使父死不葬。安得祭墓而行乎。马迁传伯夷。其言自相矛盾。不必多辨。然因此而遂疑夷齐叩马之事则恐不可。不惟程朱之说如此。饿于首阳。非君不事。屡为孔孟所称。至于求仁得仁一语。直明夷齐之心事。谏伐之举。乃所以存万世君臣之大防。又安敢不信乎。特以其言出于传说。或不无差误。马迁不暇裁择。因致后人之惑也。
上问曰。惟天地万物父母。大父母之无私。其化生万物也。壹均赋与。而人则独灵于物。圣则最灵于人。若有厚薄于其间何欤。人为万物之灵。则此灵字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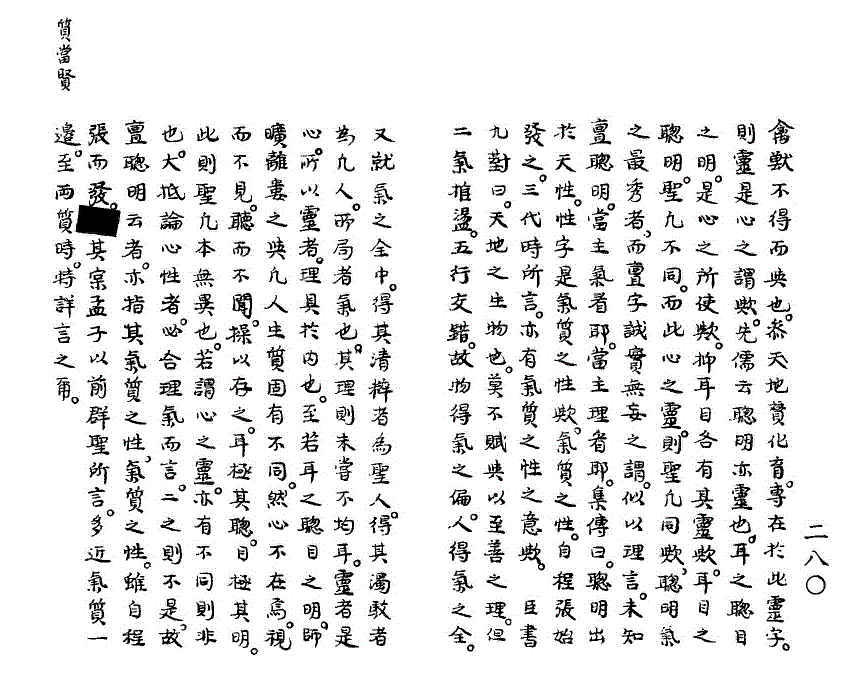 禽兽不得而与也。参天地赞化育。专在于此灵字。则灵是心之谓欤。先儒云聪明亦灵也。耳之聪目之明。是心之所使欤。抑耳目各有其灵欤。耳目之聪明。圣凡不同。而此心之灵。则圣凡同欤。聪明气之最秀者。而亶字诚实无妄之谓。似以理言。未知亶聪明。当主气看耶。当主理看耶。集传曰。聪明出于天性。性字是气质之性欤。气质之性。自程张始发之。三代时所言。亦有气质之性之意欤。
禽兽不得而与也。参天地赞化育。专在于此灵字。则灵是心之谓欤。先儒云聪明亦灵也。耳之聪目之明。是心之所使欤。抑耳目各有其灵欤。耳目之聪明。圣凡不同。而此心之灵。则圣凡同欤。聪明气之最秀者。而亶字诚实无妄之谓。似以理言。未知亶聪明。当主气看耶。当主理看耶。集传曰。聪明出于天性。性字是气质之性欤。气质之性。自程张始发之。三代时所言。亦有气质之性之意欤。臣书九对曰。天地之生物也。莫不赋与以至善之理。但二气推荡。五行交错。故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全。又就气之全中。得其清粹者为圣人。得其浊驳者为凡人。所局者气也。其理则未尝不均耳。灵者是心。所以灵者。理具于内也。至若耳之聪目之明。师旷离娄之与凡人生质固有不同。然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操以存之。耳极其聪。目极其明。此则圣凡本无异也。若谓心之灵。亦有不同则非也。大抵论心性者。必合理气而言。二之则不是。故亶聪明云者。亦指其气质之性。气质之性。虽自程张而发■(一作之)。其宲孟子以前群圣所言。多近气质一边。至两贤时。特详言之尔。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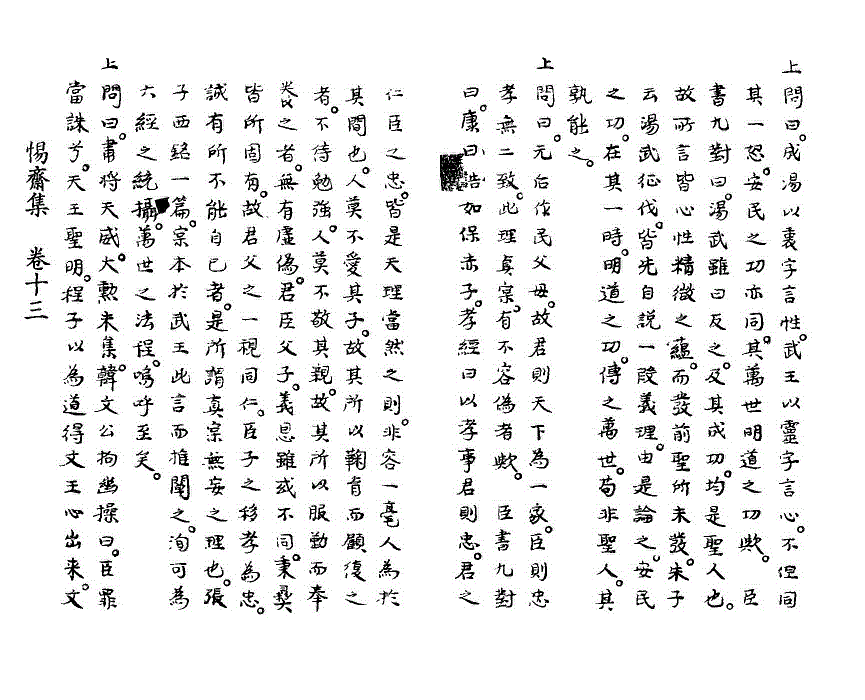 上问曰。成汤以衷字言性。武王以灵字言心。不但同其一恕。安民之功亦同。其万世明道之功欤。
上问曰。成汤以衷字言性。武王以灵字言心。不但同其一恕。安民之功亦同。其万世明道之功欤。臣书九对曰。汤武虽曰反之。及其成功。均是圣人也。故所言皆心性精微之蕴。而发前圣所未发。朱子云汤武征伐。皆先自说一段义理。由是论之。安民之功。在其一时。明道之功。传之万世。苟非圣人。其孰能之。
上问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君则天下为一家。臣则忠孝无二致。此理真宲。有不容伪者欤。
臣书九对曰。康诰曰如保赤子。孝经曰以孝事君则忠。君之仁臣之忠。皆是天理当然之则。非容一毫人为于其间也。人莫不爱其子。故其所以鞠育而顾复之者。不待勉强。人莫不敬其亲。故其所以服勤而奉养之者。无有虚伪。君臣父子。义恩虽或不同。秉彝皆所固有。故君父之一视同仁。臣子之移孝为忠。诚有所不能自已者。是所谓真宲无妄之理也。张子西铭一篇。宲本于武王此言而推阐之。洵可为六经之统摄。万世之法程。呜呼至矣。
上问曰。肃将天威。大勋未集。韩文公拘幽操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以为道得文王心出来。文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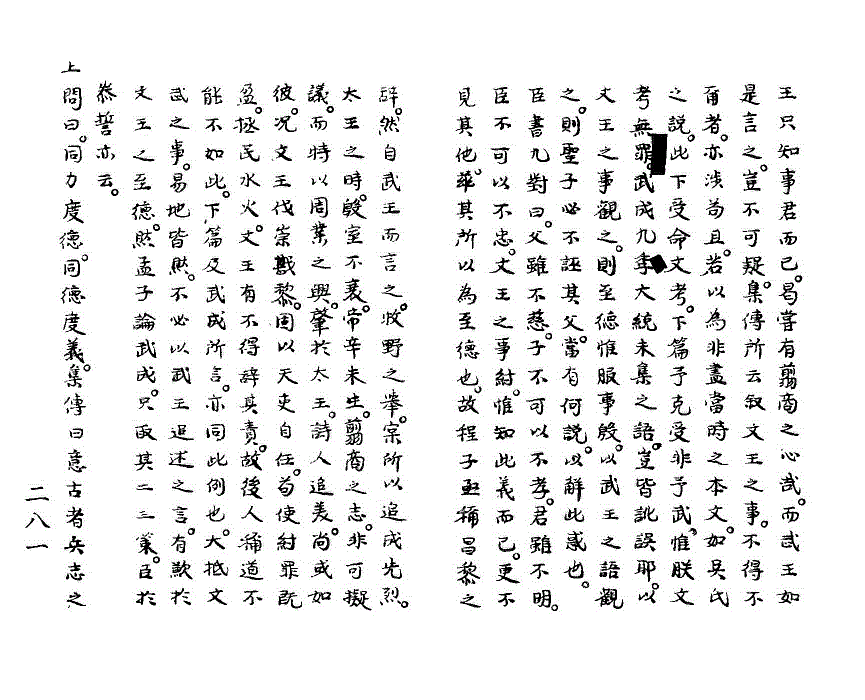 王只知事君而已。曷尝有剪商之心哉。而武王如是言之。岂不可疑。集传所云叙文王之事。不得不尔者。亦涉苟且。若以为非尽当时之本文。如吴氏之说。此下受命文考。下篇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武成九䄵大统未集之语。岂皆讹误耶。以文王之事观之。则至德惟服事殷。以武王之语观之。则圣子必不诬其父。当有何说。以解此惑也。
王只知事君而已。曷尝有剪商之心哉。而武王如是言之。岂不可疑。集传所云叙文王之事。不得不尔者。亦涉苟且。若以为非尽当时之本文。如吴氏之说。此下受命文考。下篇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武成九䄵大统未集之语。岂皆讹误耶。以文王之事观之。则至德惟服事殷。以武王之语观之。则圣子必不诬其父。当有何说。以解此惑也。臣书九对曰。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虽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文王之事纣。惟知此义而已。更不见其他。玆其所以为至德也。故程子亟称昌黎之辞。然自武王而言之。牧野之举。宲所以追成先烈。太王之时。殷室不衰。帝辛未生。剪商之志。非可拟议。而特以周业之兴。肇于太王。诗人追美。尚或如彼。况文王伐崇戡黎。固以天吏自任。苟使纣罪既盈。拯民水火。文王有不得辞其责。故后人称道不能不如此。下篇及武成所言。亦同此例也。大抵文武之事。易地皆然。不必以武王追述之言。有歉于文王之至德。然孟子论武成。只取其二三策。臣于泰誓亦云。
上问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集传曰意古者兵志之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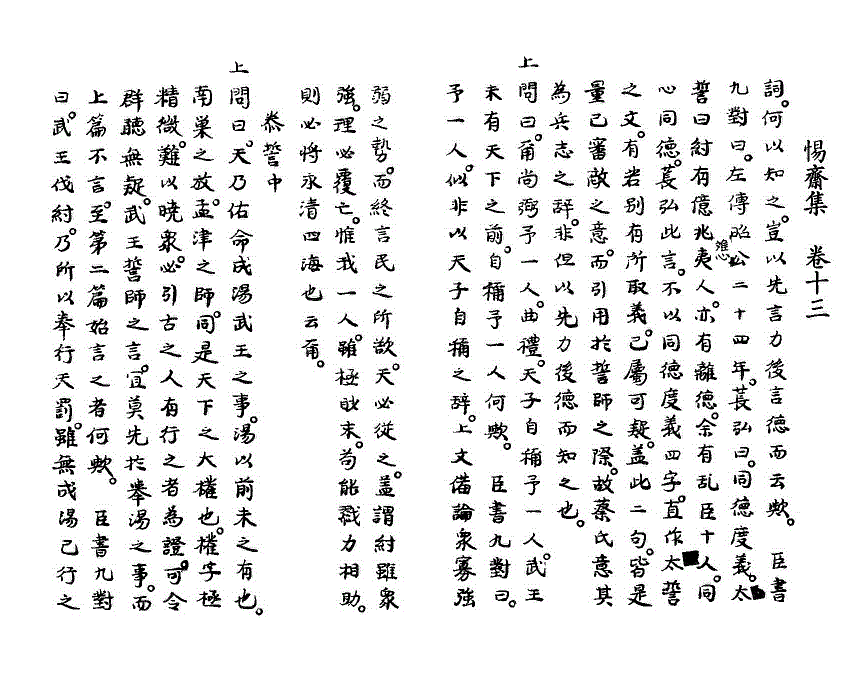 词。何以知之。岂以先言力后言德而云欤。
词。何以知之。岂以先言力后言德而云欤。臣书九对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苌弘曰。同德度义。太誓曰纣有亿兆离心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苌弘此言。不以同德度义四字。直作太誓之文。有若别有所取义。已属可疑。盖此二句。皆是量己审敌之意。而引用于誓师之际。故蔡氏意其为兵志之辞。非但以先力后德而知之也。
上问曰。尔尚弼予一人。曲礼。天子自称予一人。武王未有天下之前。自称予一人何欤。
臣书九对曰。予一人。似非以天子自称之辞。上文备论众寡强弱之势。而终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盖谓纣虽众强。理必覆亡。惟我一人。虽极眇末。苟能戮力相助。则必将永清四海也云尔。
泰誓中
上问曰。天乃佑命成汤武王之事。汤以前未之有也。南巢之放。孟津之师。同是天下之大权也。权字极精微。难以晓众。必引古之人有行之者为證。可令群听无疑。武王誓师之言。宜莫先于举汤之事。而上篇不言。至第二篇始言之者何欤。
臣书九对曰。武王伐纣。乃所以奉行天罚。虽无成汤已行之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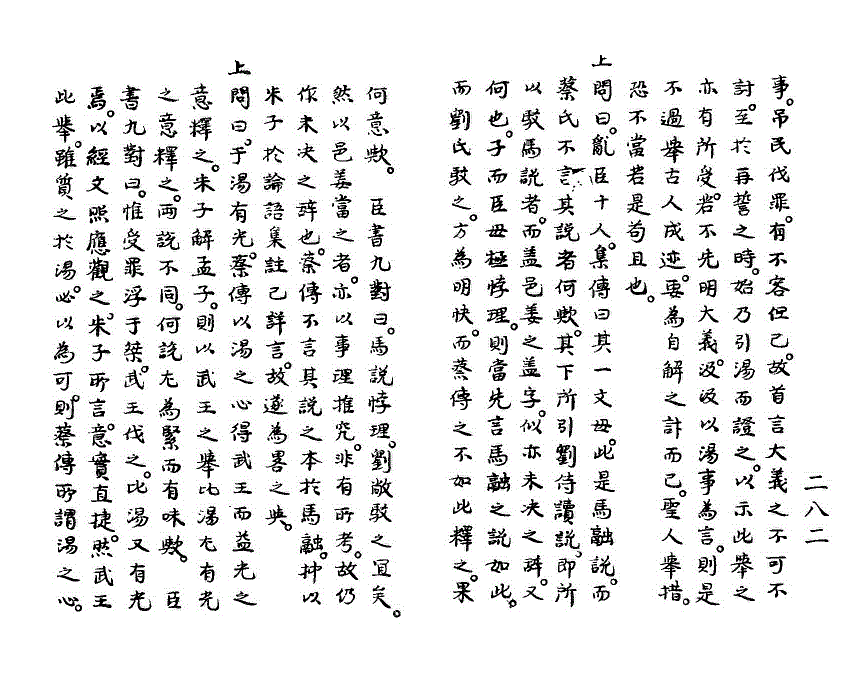 事。吊民伐罪。有不容但已。故首言大义之不可不讨。至于再誓之时。始乃引汤而證之。以示此举之亦有所受。若不先明大义。汲汲以汤事为言。则是不过举古人成迹。要为自解之计而已。圣人举措。恐不当若是苟且也。
事。吊民伐罪。有不容但已。故首言大义之不可不讨。至于再誓之时。始乃引汤而證之。以示此举之亦有所受。若不先明大义。汲汲以汤事为言。则是不过举古人成迹。要为自解之计而已。圣人举措。恐不当若是苟且也。上问曰。乱臣十人。集传曰其一文母。此是马融说。而蔡氏不言其说者何欤。其下所引刘侍读说。即所以驳马说者。而盖邑姜之盖字。似亦未决之辞。又何也。子而臣母极悖理。则当先言马融之说如此。而刘氏驳之。方为明快。而蔡传之不如此释之。果何意欤。
臣书九对曰。马说悖理。刘敞驳之宜矣。然以邑姜当之者。亦以事理推究。非有所考。故仍作未决之辞也。蔡传不言其说之本于马融。抑以朱子于论语集注已详言。故遂为略之与。
上问曰。于汤有光。蔡传以汤之心得武王而益光之意释之。朱子解孟子。则以武王之举比汤尤有光之意释之。两说不同。何说尤为紧而有味欤。
臣书九对曰。惟受罪浮于桀。武王伐之。比汤又有光焉。以经文照应观之。朱子所言。意实直捷。然武王此举。虽质之于汤。必以为可。则蔡传所谓汤之心。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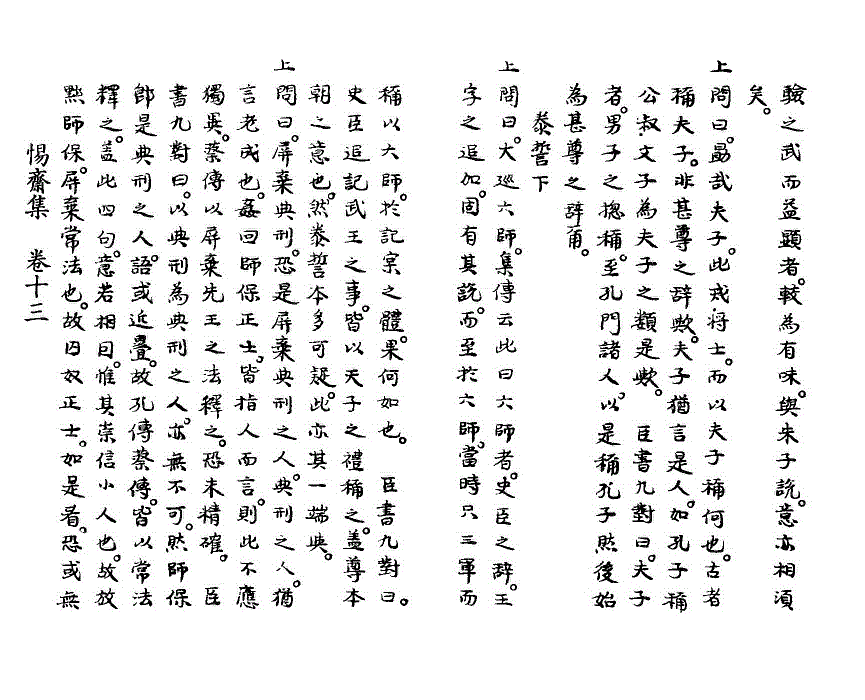 验之武而益显者。较为有味。与朱子说。意亦相须矣。
验之武而益显者。较为有味。与朱子说。意亦相须矣。上问曰。勖哉夫子。此戒将士。而以夫子称何也。古者称夫子。非甚尊之辞欤。夫子犹言是人。如孔子称公叔文子为夫子之类是欤。
臣书九对曰。夫子者。男子之揔称。至孔门诸人。以是称孔子然后始为甚尊之辞尔。
泰誓下
上问曰。大巡六师。集传云此曰六师者。史臣之辞。王字之追加。固有其说。而至于六师。当时只三军而称以六师。于记宲之体。果何如也。
臣书九对曰。史臣追记武王之事。皆以天子之礼称之。盖尊本朝之意也。然泰誓本多可疑。此亦其一端与。
上问曰。屏弃典刑。恐是屏弃典刑之人。典刑之人。犹言老成也。奸回师保正士。皆指人而言。则此不应独异。蔡传以屏弃先王之法释之。恐未精确。
臣书九对曰。以典刑为典刑之人。亦无不可。然师保即是典刑之人。语或近叠。故孔传蔡传。皆以常法释之。盖此四句。意若相因。惟其崇信小人也。故放黜师保。屏弃常法也。故囚奴正士。如是看。恐或无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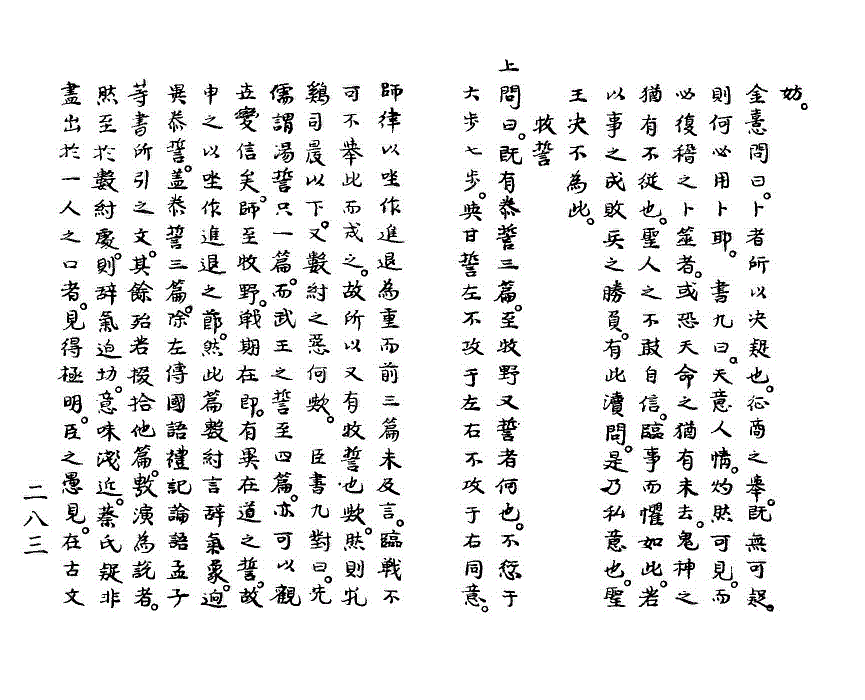 妨。
妨。金憙问曰。卜者所以决疑也。征商之举。既无可疑。则何必用卜耶。
书九曰。天意人情。灼然可见。而必复稽之卜筮者。或恐天命之犹有未去。鬼神之犹有不从也。圣人之不敢自信。临事而惧如此。若以事之成败兵之胜负。有此渎问。是乃私意也。圣王决不为此。
牧誓
上问曰。既有泰誓三篇。至牧野又誓者何也。不愆于六步七步。与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同意。师律以坐作进退为重而前三篇未及言。临战不可不举此而戒之。故所以又有牧誓也欤。然则牝鸡司晨以下。又数纣之恶何欤。
臣书九对曰。先儒谓汤誓只一篇。而武王之誓至四篇。亦可以观世变信矣。师至牧野。战期在即。有异在道之誓。故申之以坐作进退之节。然此篇数纣言辞气象。迥异泰誓。盖泰誓三篇。除左传国语礼记论语孟子等书所引之文。其馀殆若掇拾他篇。敷演为说者。然至于数纣处。则辞气迫切。意味浅近。蔡氏疑非尽出于一人之口者。见得极明。臣之愚见。在古文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4H 页
 中最似可疑。然则此篇之略数纣恶。政可见武王不得已之心也与。
中最似可疑。然则此篇之略数纣恶。政可见武王不得已之心也与。上问曰。司马,司徒,司空。此时吕尚为司马欤。武王时为诸侯。故只三卿。而诸侯之邦。无冢宰,宗伯,司寇。则邦治礼刑。谁掌之欤。抑一卿兼二事欤。一卿兼二事。则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司寇。司空兼宗伯欤。古之官制。可详考而言欤。
臣书九对曰。立政举文武时事。只有司徒司马司空。与此篇合。可知其不立六卿。而史记但云太公望为师。其为司马则不可考矣。周制诸侯三卿。注礼者云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然左传鲁三卿。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而又有臧孙纥为司寇。夏父弗忌为宗伯。羽父求为太宰。则六卿俱备。并非兼官。故或据尚书大传谓天子三公。皆六卿为之。而分为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马。三司寇司空。而取每等之下者以为名。故曰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由此推之。侯国三卿。必仿其制。虽六卿俱备。而秪以三官为名也。此说似可取。
上问曰。色荒甘酒。其祸孰大。微子言纣之恶曰。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以此观之。纣之败德。专由于酒。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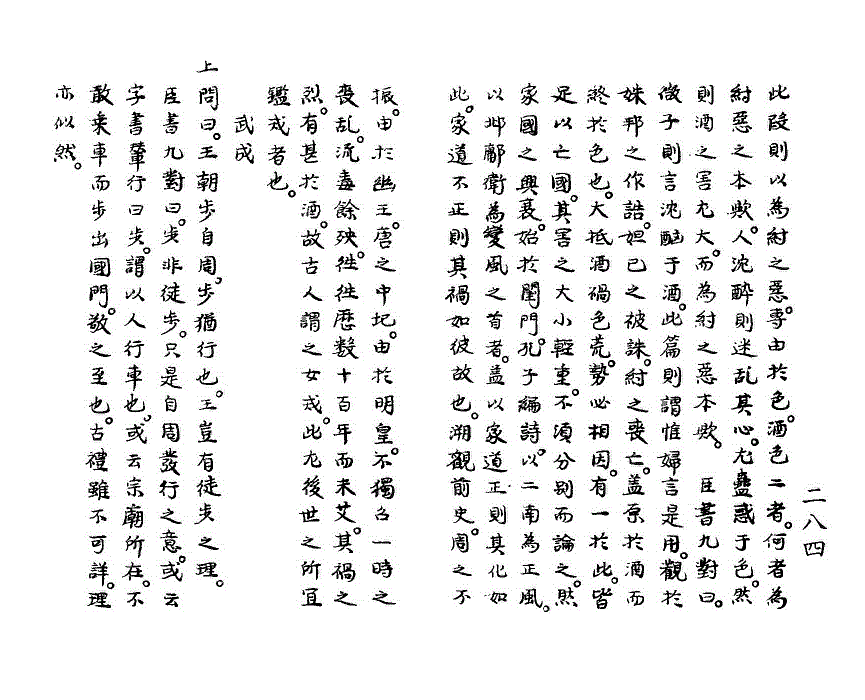 此段则以为纣之恶。专由于色。酒色二者。何者为纣恶之本欤。人沈醉则迷乱其心。尤蛊惑于色。然则酒之害尤大。而为纣之恶本欤。
此段则以为纣之恶。专由于色。酒色二者。何者为纣恶之本欤。人沈醉则迷乱其心。尤蛊惑于色。然则酒之害尤大。而为纣之恶本欤。臣书九对曰。微子则言沈酗于酒。此篇则谓惟妇言是用。观于姝邦之作诰。妲己之被诛。纣之丧亡。盖原于酒而终于色也。大抵酒祸色荒。势必相因。有一于此。皆足以亡国。其害之大小轻重。不须分别而论之。然家国之兴衰。始于闺门。孔子编诗。以二南为正风。以邶鄘卫为变风之首者。盖以家道正则其化如此。家道不正则其祸如彼故也。溯观前史。周之不振。由于幽王。唐之中圮。由于明皇。不独召一时之丧乱。流毒馀殃。往往历数十百年而未艾。其祸之烈。有甚于酒。故古人谓之女戒。此尤后世之所宜鉴戒者也。
武成
上问曰。王朝步自周。步犹行也。王岂有徒步之理。
臣书九对曰。步非徒步。只是自周发行之意。或云字书辇行曰步。谓以人行车也。或云宗庙所在。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古礼虽不可详。理亦似然。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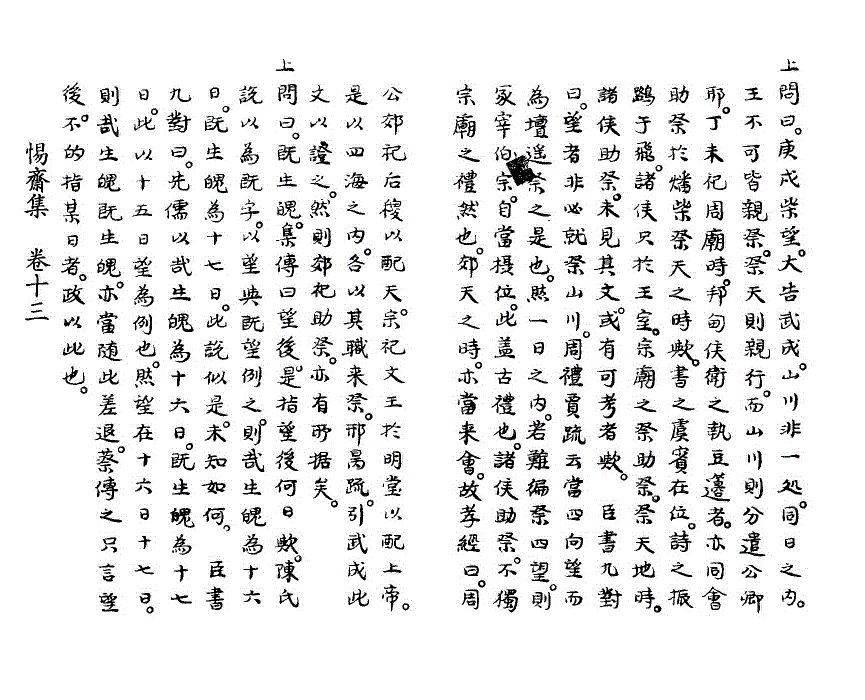 上问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山川非一处。同日之内。王不可皆亲祭。祭天则亲行。而山川则分遣公卿耶。丁未祀周庙时。邦甸侯卫之执豆笾者。亦同会助祭于燔柴祭天之时欤。书之虞宾在位。诗之振𪆽于飞。诸侯只于王室。宗庙之祭助祭。祭天地时。诸侯助祭。未见其文。或有可考者欤。
上问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山川非一处。同日之内。王不可皆亲祭。祭天则亲行。而山川则分遣公卿耶。丁未祀周庙时。邦甸侯卫之执豆笾者。亦同会助祭于燔柴祭天之时欤。书之虞宾在位。诗之振𪆽于飞。诸侯只于王室。宗庙之祭助祭。祭天地时。诸侯助祭。未见其文。或有可考者欤。臣书九对曰。望者非必就祭山川。周礼贾疏云当四向望而为坛遥祭之是也。然一日之内。若难遍祭四望。则冢宰宗伯。自当摄位。此盖古礼也。诸侯助祭。不独宗庙之礼然也。郊天之时。亦当来会。故孝经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邢炳疏。引武成此文以證之。然则郊祀助祭。亦有所据矣。
上问曰。既生魄。集传曰望后。是指望后何日欤。陈氏说以为既字。以望与既望例之。则哉生魄为十六日。既生魄为十七日。此说似是。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先儒以哉生魄为十六日。既生魄为十七日。此以十五日望为例也。然望在十六日十七日。则哉生魄既生魄。亦当随此差退。蔡传之只言望后。不的指某日者。政以此也。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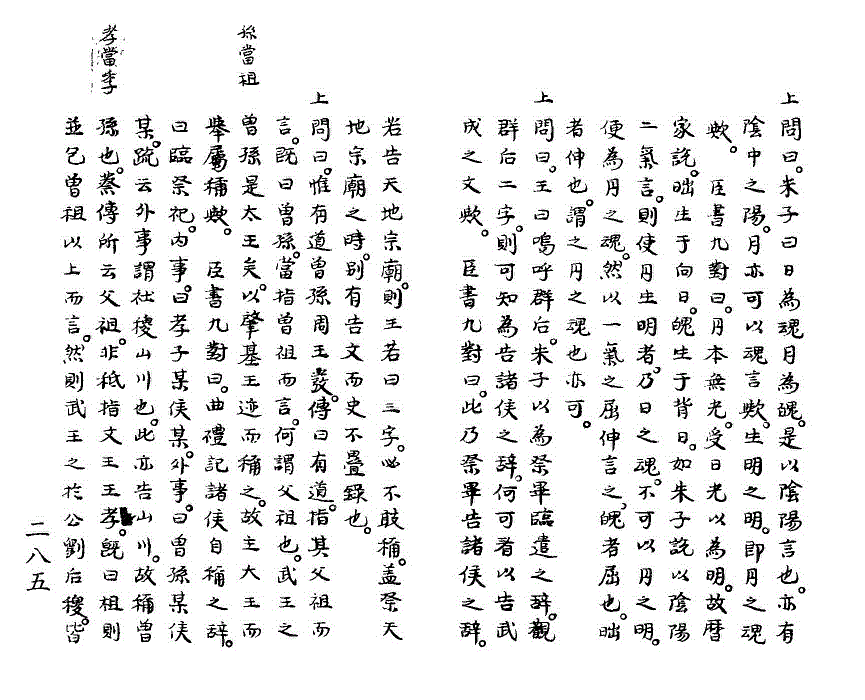 上问曰。朱子曰日为魂月为魄。是以阴阳言也。亦有阴中之阳。月亦可以魂言欤。生明之明。即月之魂欤。
上问曰。朱子曰日为魂月为魄。是以阴阳言也。亦有阴中之阳。月亦可以魂言欤。生明之明。即月之魂欤。臣书九对曰。月本无光。受日光以为明。故历家说。昢生于向日。魄生于背日。如朱子说以阴阳二气言。则使月生明者。乃日之魂。不可以月之明。便为月之魂。然以一气之屈伸言之。魄者屈也。昢者伸也。谓之月之魂也亦可。
上问曰。王曰呜呼群后。朱子以为祭毕临遣之辞。观群后二字。则可知为告诸侯之辞。何可看以告武成之文欤。
臣书九对曰。此乃祭毕告诸侯之辞。若告天地宗庙。则王若曰三字。必不敢称。盖祭天地宗庙之时。别有告文而史不叠录也。
上问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传曰有道。指其父祖而言。既曰曾孙。当指曾祖而言。何谓父祖也。武王之曾祖是太王矣。以肇基王迹而称之。故主大王而举属称欤。
臣书九对曰。曲礼记诸侯自称之辞。曰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疏云外事谓社稷山川也。此亦告山川。故称曾孙也。蔡传所云父祖。非秪指文王王季。既曰祖则并包曾祖以上而言。然则武王之于公刘后稷。皆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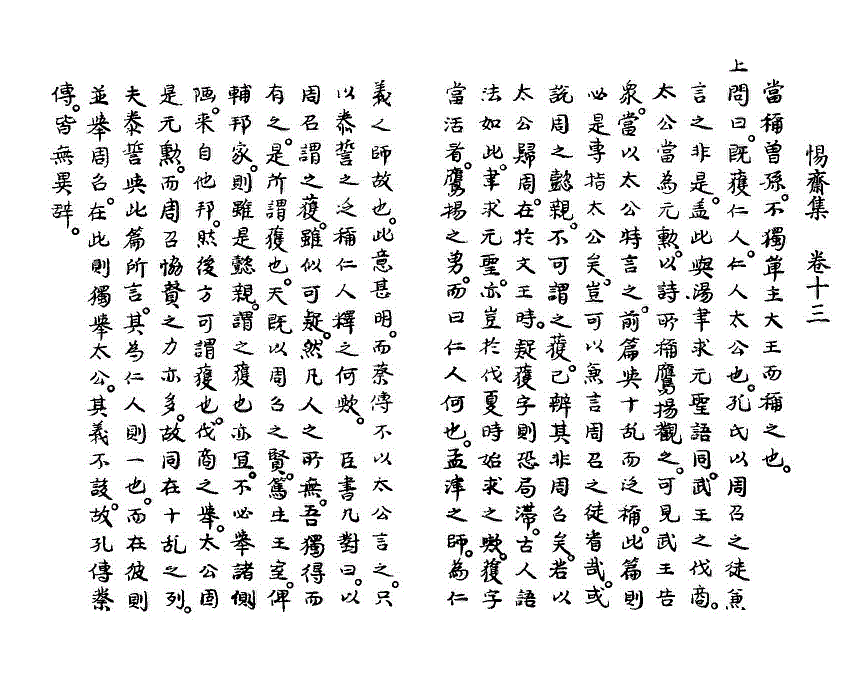 当称曾孙。不独单主大王而称之也。
当称曾孙。不独单主大王而称之也。上问曰。既获仁人。仁人太公也。孔氏以周召之徒兼言之非是。盖此与汤聿求元圣语同。武王之伐商。太公当为元勋。以诗所称鹰扬观之。可见武王告众。当以太公特言之。前篇与十乱而泛称。此篇则必是专指太公矣。岂可以兼言周召之徒看哉。或说周之懿亲。不可谓之获。已辨其非周召矣。若以太公归周。在于文王时。疑获字则恐局滞。古人语法如此。聿求元圣。亦岂于伐夏时始求之欤。获字当活看。鹰扬之勇。而曰仁人何也。孟津之师。为仁义之师故也。此意甚明。而蔡传不以太公言之。只以泰誓之泛称仁人释之何欤。
臣书九对曰。以周召谓之获。虽似可疑。然凡人之所无。吾独得而有之。是所谓获也。天既以周召之贤。笃生王室。俾辅邦家。则虽是懿亲。谓之获也亦宜。不必举诸侧陋。来自他邦。然后方可谓获也。伐商之举。太公固是元勋。而周召协赞之力亦多。故同在十乱之列。夫泰誓与此篇所言。其为仁人则一也。而在彼则并举周召。在此则独举太公。其义不该。故孔传蔡传。皆无异辞。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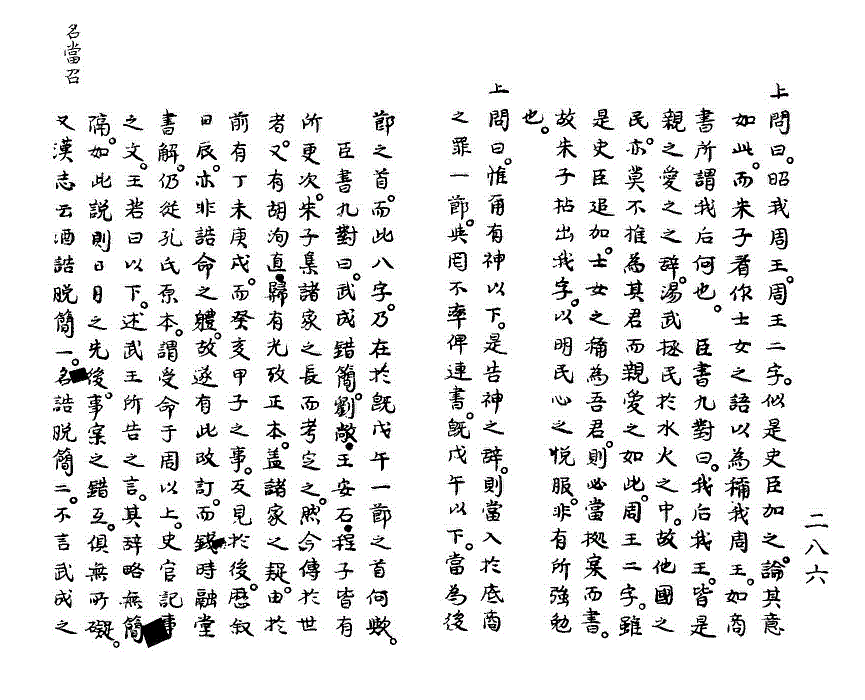 上问曰。昭我周王。周王二字。似是史臣加之。论其意如此。而朱子看作士女之语以为称我周王。如商书所谓我后何也。
上问曰。昭我周王。周王二字。似是史臣加之。论其意如此。而朱子看作士女之语以为称我周王。如商书所谓我后何也。臣书九对曰。我后我王。皆是亲之爱之之辞。汤武拯民于水火之中。故他国之民。亦莫不推为其君而亲爱之如此。周王二字。虽是史臣追加。士女之称为吾君。则必当据宲而书。故朱子拈出我字。以明民心之悦服。非有所强勉也。
上问曰。惟尔有神以下。是告神之辞。则当入于底商之罪一节。与罔不率俾连书。既戊午以下。当为后节之首。而此八字。乃在于既戊午一节之首何欤。
臣书九对曰。武成错简。刘敞,王安石,程子皆有所更次。朱子集诸家之长而考定之。然今传于世者。又有胡洵直,归有光考正本。盖诸家之疑。由于前有丁未庚戌。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见于后。历叙日辰。亦非诰命之体。故遂有此改订。而钱时融堂书解。仍从孔氏原本。谓受命于周以上。史官记事之文。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之言。其辞略无简隔。如此说则日月之先后。事宲之错互。俱无所碍。又汉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不言武成之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7H 页
 有脱简。姑存钱说。以备一解。恐无不可。蔡氏以惟尔有神以下十六字。不属于罔不率俾之下者。经文既从原本次第。而此句上。有恭天成名一节。固不得越次联属。若朱子考定本。文势已自相接矣。
有脱简。姑存钱说。以备一解。恐无不可。蔡氏以惟尔有神以下十六字。不属于罔不率俾之下者。经文既从原本次第。而此句上。有恭天成名一节。固不得越次联属。若朱子考定本。文势已自相接矣。上问曰。式商容闾。只是过其门。凭轼而已。非表厥宅里之谓。而集传曰表其闾。有若后世㫌门之称何欤。
臣书九对曰。此虽云式商容闾。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皆言表商容之闾。集传盖据此为说也。
上问曰。惟食丧祭。食足而后。可以慎终。可以报本。发粟散财。特一时之事耳。武王何以使天下之民。足其食而丧祭尽礼欤。必有其道。愿闻之。
臣书九对曰。圣王治民。未有不富而教之者。故画井分区。以制其产。省徭薄赋。以养其力。通功易事。以赡其用。赈穷恤贫。以安其生。然后劝之以九歌。防之以五礼。则民莫不兴善惩恶。各率其教。此孟子所谓王道之始也。周室之先。积德累仁。而公刘之彻田为粮。文王之发仓赈饥。尤是兴王之本。武王克修先业。使圣人正德利用厚生之道莫不毕备。故天下无有不从。而民德皆归于厚矣。至于发粟散财。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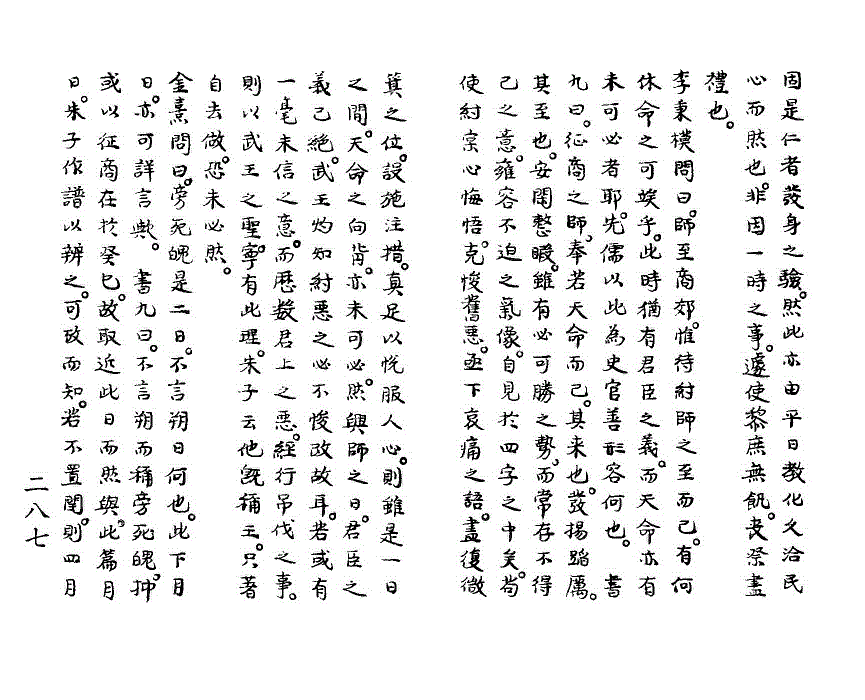 固是仁者发身之验。然此亦由平日教化久洽民心而然也。非因一时之事。遽使黎庶无饥。丧祭尽礼也。
固是仁者发身之验。然此亦由平日教化久洽民心而然也。非因一时之事。遽使黎庶无饥。丧祭尽礼也。李秉模问曰。师至商郊。惟待纣师之至而已。有何休命之可俟乎。此时犹有君臣之义。而天命亦有未可必者耶。先儒以此为史官善形容何也。
书九曰。征商之师。奉若天命而已。其来也。发扬蹈厉。其至也。安闲整暇。虽有必可胜之势。而常存不得已之意。雍容不迫之气像。自见于四字之中矣。苟使纣宲心悔悟。克悛旧恶。亟下哀痛之语。尽复微箕之位。设施注措。真足以悦服人心。则虽是一日之间。天命之向背。亦未可必。然兴师之日。君臣之义已绝。武王灼知纣恶之必不悛改故耳。若或有一毫未信之意。而历数君上之恶。经行吊伐之事。则以武王之圣。宁有此理。朱子云他既称王。只著自去做。恐未必然。
金熹问曰。旁死魄是二日。不言朔日何也。此下月日。亦可详言欤。
书九曰。不言朔而称旁死魄。抑或以征商在于癸巳。故取近此日而然与。此篇月日。朱子作谱以辨之。可考而知。若不置闰。则四月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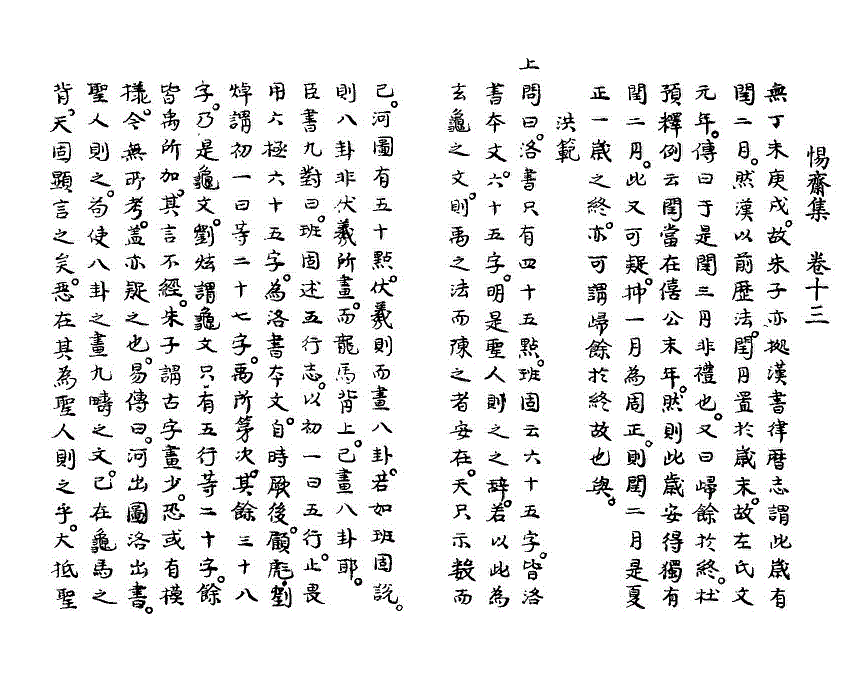 无丁未庚戌。故朱子亦据汉书律历志谓此岁有闰二月。然汉以前历法。闰月置于岁末。故左氏文元年。传曰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又曰归馀于终。杜预释例云闰当在僖公末年。然则此岁安得独有闰二月。此又可疑。抑一月为周正。则闰二月是夏正一岁之终。亦可谓归馀于终故也与。
无丁未庚戌。故朱子亦据汉书律历志谓此岁有闰二月。然汉以前历法。闰月置于岁末。故左氏文元年。传曰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又曰归馀于终。杜预释例云闰当在僖公末年。然则此岁安得独有闰二月。此又可疑。抑一月为周正。则闰二月是夏正一岁之终。亦可谓归馀于终故也与。洪范
上问曰。洛书只有四十五点。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六十五字。明是圣人则之之辞。若以此为玄龟之文。则禹之法而陈之者安在。天只示数而已。河图有五十点。伏羲则而画八卦。若如班固说。则八卦非伏羲所画。而龙马背上。已画八卦耶。
臣书九对曰。班固述五行志。以初一曰五行。止畏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自时厥后。顾彪,刘焯谓初一曰等二十七字。禹所第次。其馀三十八字。乃是龟文。刘炫谓龟文只有五行等二十字。馀皆禹所加。其言不经。朱子谓古字画少。恐或有模㨾。今无所考。盖亦疑之也。易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苟使八卦之画九畴之文。已在龟马之背。天固显言之矣。恶在其为圣人则之乎。大抵圣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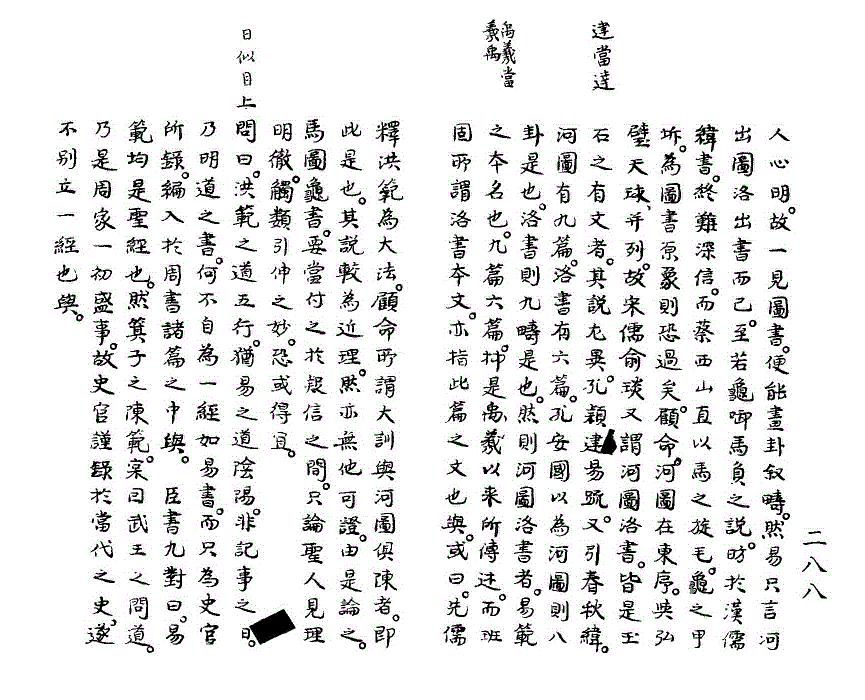 人心明。故一见图书。便能画卦叙畴。然易只言河出图洛出书而已。至若龟衔马负之说。昉于汉儒纬书。终难深信。而蔡西山直以马之旋毛。龟之甲坼。为图书原象则恐过矣。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弘璧天球并列。故宋儒俞琰又谓河图洛书。皆是玉石之有文者。其说尤异。孔颖达易疏。又引春秋纬。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河图洛书者。易范之本名也。九篇六篇。抑是羲禹以来所传述。而班固所谓洛书本文。亦指此篇之文也与。或曰。先儒释洪范为大法。顾命所谓大训与河图俱陈者。即此是也。其说较为近理。然亦无他可證。由是论之。马图龟书。要当付之于疑信之间。只论圣人见理明彻。触类引伸之妙。恐或得宜。
人心明。故一见图书。便能画卦叙畴。然易只言河出图洛出书而已。至若龟衔马负之说。昉于汉儒纬书。终难深信。而蔡西山直以马之旋毛。龟之甲坼。为图书原象则恐过矣。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弘璧天球并列。故宋儒俞琰又谓河图洛书。皆是玉石之有文者。其说尤异。孔颖达易疏。又引春秋纬。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河图洛书者。易范之本名也。九篇六篇。抑是羲禹以来所传述。而班固所谓洛书本文。亦指此篇之文也与。或曰。先儒释洪范为大法。顾命所谓大训与河图俱陈者。即此是也。其说较为近理。然亦无他可證。由是论之。马图龟书。要当付之于疑信之间。只论圣人见理明彻。触类引伸之妙。恐或得宜。上问曰。洪范之道五行。犹易之道阴阳。非记事之日(日似目)。乃明道之书。何不自为一经如易书。而只为史官所录。编入于周书诸篇之中与。
臣书九对曰。易范均是圣经也。然箕子之陈范。宲因武王之问道。乃是周家一初盛事。故史官谨录于当代之史。遂不别立一经也与。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9H 页
 上问曰。易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拘羑里而演易矣。箕子亦于在囚之时。推演此书。及武王问而取以陈之欤。抑初未尝成书。至武王问而后。始撰次文字与。
上问曰。易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拘羑里而演易矣。箕子亦于在囚之时。推演此书。及武王问而取以陈之欤。抑初未尝成书。至武王问而后。始撰次文字与。臣书九对曰。箕子叙范。如文王之演易。平日述作之有无。虽不可详。义理讲究。必当精熟。故及夫武王之问。敷演陈说。穷极微奥。可见其一部成书具在胸中。而得之于忧患困苦之中者。固已多矣。
上问曰。自太师来而吾道东。八条之教。民到于今受赐。东儒之所当尊信表章者。尤在是书。而罗丽之间。寥寥乎无闻。我朝诸贤。谁最发挥之与。
臣书九对曰。箕子之来。即吾东万世之幸。田蚕织作之教。八政所以厚其生也。礼义贞信之风。三德所以乂其性也。凡其化民成俗者。皆本于洪范。则大法之行。宲与周家同时。罗丽以来。遗泽寝漠。至于我朝。 圣作神承。皇极之道。复明于世。而儒贤辈出。莫不潜心性理之学。从事诚正之工。虽未尝以洪范一篇。专力独治。要其归宿。亦不外乎是事之范围。故先正文成公臣李珥尝作箕子宲纪。文元公臣金长生又尝建白于朝。欲尊崇箕子。同于孔庙。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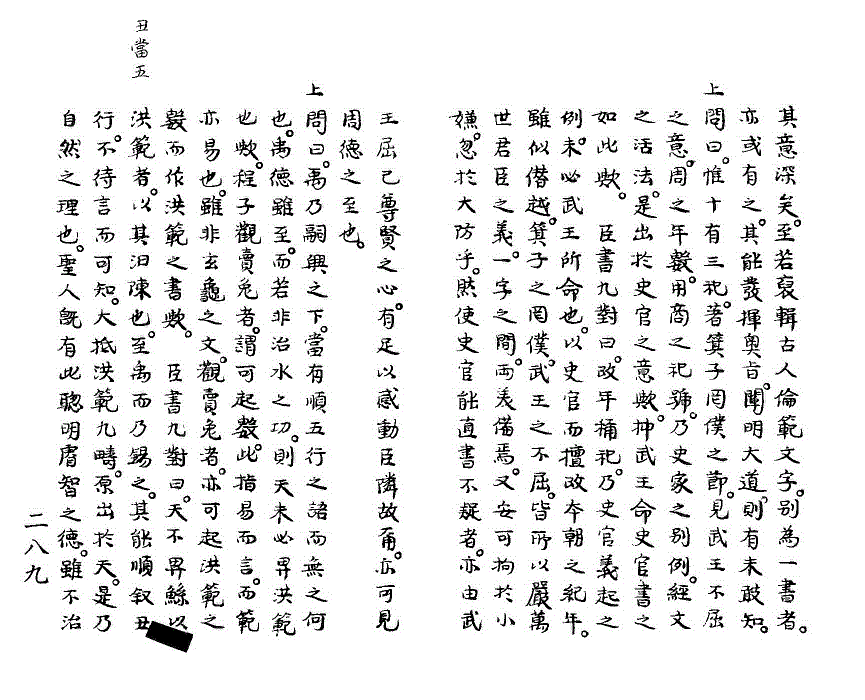 其意深矣。至若裒辑古人伦范文字。别为一书者。亦或有之。其能发挥奥旨。阐明大道。则有未敢知。
其意深矣。至若裒辑古人伦范文字。别为一书者。亦或有之。其能发挥奥旨。阐明大道。则有未敢知。上问曰。惟十有三祀。著箕子罔仆之节。见武王不屈之意。周之年数。用商之祀号。乃史家之别例。经文之活法。是出于史官之意欤。抑武王命史官书之如此欤。
臣书九对曰。改年称祀。乃史官义起之例。未必武王所命也。以史官而擅改本朝之纪年。虽似僭越。箕子之罔仆。武王之不屈。皆所以严万世君臣之义。一字之间。两美备焉。又安可拘于小嫌。忽于大防乎。然使史官能直书不疑者。亦由武王屈己尊贤之心。有足以感动臣邻故尔。亦可见周德之至也。
上问曰。禹乃嗣兴之下。当有顺五行之语而无之何也。禹德虽至。而若非治水之功。则天未必畀洪范也欤。程子观卖兔者。谓可起数。此指易而言。而范亦易也。虽非玄龟之文。观卖兔者。亦可起洪范之数而作洪范之书欤。
臣书九对曰。天不畀鲧以洪范者。以其汩陈也。至禹而乃锡之。其能顺叙五行。不待言而可知。大抵洪范九畴。原出于天。是乃自然之理也。圣人既有此聪明睿智之德。虽不治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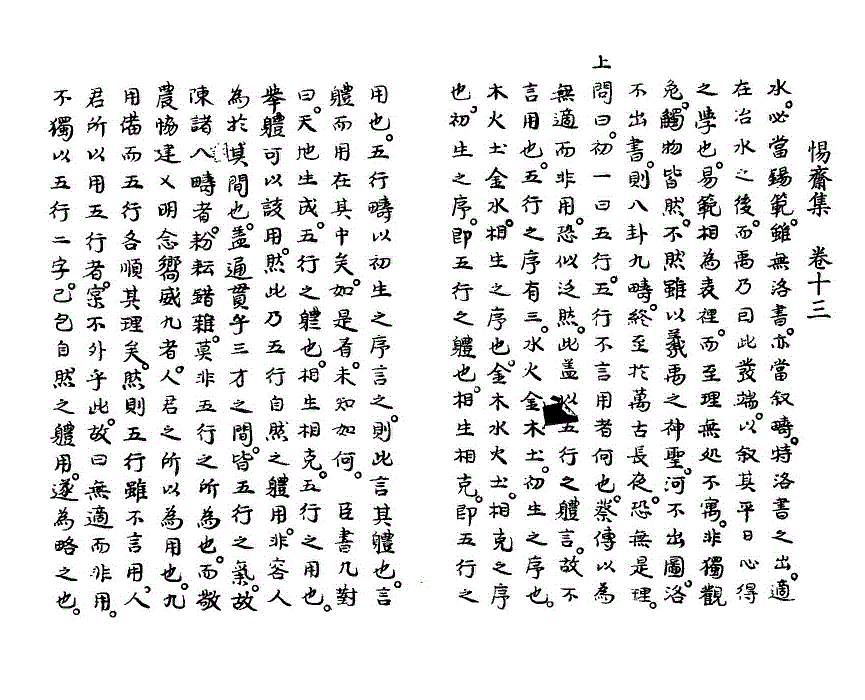 水。必当锡范。虽无洛书。亦当叙畴。特洛书之出。适在治水之后。而禹乃因此发端。以叙其平日心得之学也。易范相为表里。而至理无处不寓。非独观兔。触物皆然。不然虽以羲禹之神圣。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则八卦九畴。终至于万古长夜。恐无是理。
水。必当锡范。虽无洛书。亦当叙畴。特洛书之出。适在治水之后。而禹乃因此发端。以叙其平日心得之学也。易范相为表里。而至理无处不寓。非独观兔。触物皆然。不然虽以羲禹之神圣。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则八卦九畴。终至于万古长夜。恐无是理。上问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不言用者何也。蔡传以为无适而非用。恐似泛然。此盖以五行之体言。故不言用也。五行之序有三。水火木金土。初生之序也。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也。金木水火土。相克之序也。初生之序。即五行之体也。相生相克。即五行之用也。五行畴以初生之序言之。则此言其体也。言体而用在其中矣。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天地生成。五行之体也。相生相克。五行之用也。举体可以该用。然此乃五行自然之体用。非容人为于其间也。盖通贯乎三才之间。皆五行之气。故陈诸八畴者。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0L 页
 上问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天之所生者三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地之所生者二也。此亦参天两地之理欤。参天两地而五数起。阴阳分而为五行矣。五行五气也。不曰五气而曰五行何也。是言气之运行也。然则自其初生之时。已含流行之意欤。
上问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天之所生者三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地之所生者二也。此亦参天两地之理欤。参天两地而五数起。阴阳分而为五行矣。五行五气也。不曰五气而曰五行何也。是言气之运行也。然则自其初生之时。已含流行之意欤。臣书九对曰。阳象圆。圆者经(经似径。下皆仿此。)一而围三。阴象方。方者经(经似径)一而围四。奇数则以一为一。耦数则以二为一。故曰参天两地。而五行之生。天三地二。其数亦相沕合。理本无二故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者气也。所以动之静之者理也。有是流行之理。故气能流行。然则五行初生之时。流行之理。已具于其中。理气不离之妙。即此可见。
上问曰。润下炎上以气言。曲直从革以形质言。稼穑以德言。五行一也。而或以气言。或以形质言。或以德言何欤。水火木金。皆言其性。而土则独以德言。加爰字。异于四行之例。盖以土之无定位而然也。然土自有土之性。如欲说土之性。则当如何称欤。或曰。五行之生久矣。神农教耕之前。无稼穑。无稼穑之时。土之德何以称焉。由此论之。称以稼穑。不如直称土之性。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润下炎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1H 页
 上曲直从革。水火木金气质之性也。水火轻清。木金重浊。故或以气言。或以质言。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故元无成性。无成性者。即土之性也。邵子云土性软缓。此亦就其气质言。非土性之全德也。故土不言性。只举其德之最盛者曰稼穑。稼穑虽主五谷而言。若因此而遂谓神农教耕之前。土无可称之德。恐太拘泥。五谷之外。万物之盈于两间者。何莫非土之所生成乎。张子曰。土者地之质也。语其全体则生成是也。语其近而最切。则人生所托。民用所需。无一日之可离者。稼穑是已。故此特以其功用言之也。
上曲直从革。水火木金气质之性也。水火轻清。木金重浊。故或以气言。或以质言。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故元无成性。无成性者。即土之性也。邵子云土性软缓。此亦就其气质言。非土性之全德也。故土不言性。只举其德之最盛者曰稼穑。稼穑虽主五谷而言。若因此而遂谓神农教耕之前。土无可称之德。恐太拘泥。五谷之外。万物之盈于两间者。何莫非土之所生成乎。张子曰。土者地之质也。语其全体则生成是也。语其近而最切。则人生所托。民用所需。无一日之可离者。稼穑是已。故此特以其功用言之也。上问曰。二五事。五行之理为五常。此不言五常而言五事何也。有物而有则。形色天性也。故特言气。欲于气上见理欤。今以貌言视听思。分属五常。则果一一相合欤。貌者水。水即智。恭肃可谓之智欤。言者火。火即礼。从乂可谓之礼欤。视者木。木是仁。明哲可谓之仁欤。听者金。金是义。聪谋可谓之义欤。思者土。土是信。睿圣可谓之信欤。恭肃之为智。从乂之为礼。明哲之为仁。聪谋之为义。睿圣之为信。皆可详言欤。
臣书九对曰。人得五行之理。以为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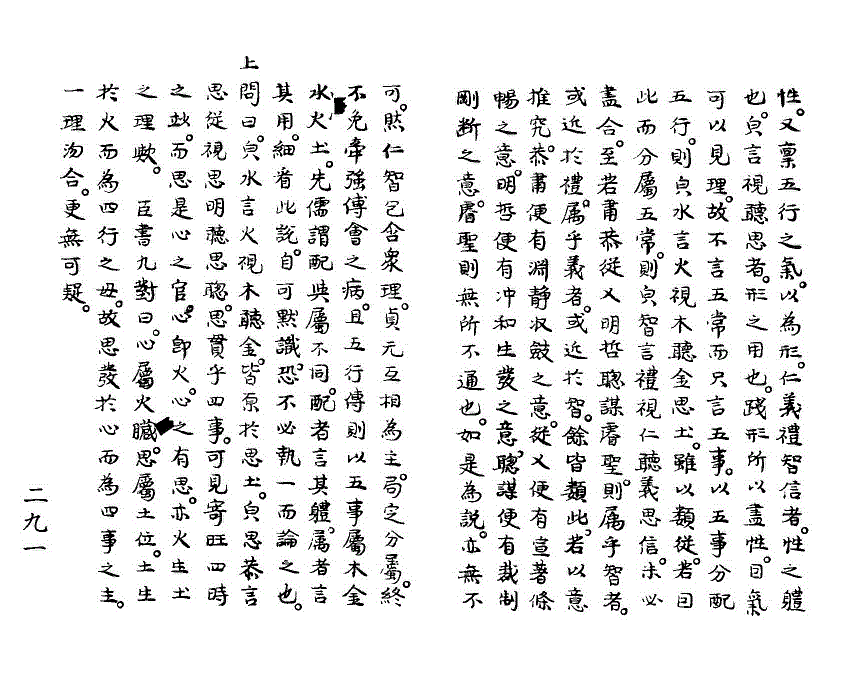 性。又禀五行之气。以为形。仁义礼智信者。性之体也。貌言视听思者。形之用也。践形所以尽性。因气可以见理。故不言五常而只言五事。以五事分配五行。则貌水言火视木听金思土。虽以类从。若因此而分属五常。则貌智言礼视仁听义思信。未必尽合。至若肃恭从乂明哲聪谋睿圣。则属乎智者。或近于礼。属乎义者。或近于智。馀皆类此。若以意推究。恭肃便有渊静收敛之意。从乂便有宣著条畅之意。明哲便有冲和生发之意。聪谋便有裁制刚断之意。睿圣则无所不通也。如是为说。亦无不可。然仁智包含众理。贞元互相为主。局定分属。终不免牵强傅会之病。且五行传则以五事属木金火水土。先儒谓配与属不同。配者言其体。属者言其用。细看此说。自可默识。恐不必执一而论之也。
性。又禀五行之气。以为形。仁义礼智信者。性之体也。貌言视听思者。形之用也。践形所以尽性。因气可以见理。故不言五常而只言五事。以五事分配五行。则貌水言火视木听金思土。虽以类从。若因此而分属五常。则貌智言礼视仁听义思信。未必尽合。至若肃恭从乂明哲聪谋睿圣。则属乎智者。或近于礼。属乎义者。或近于智。馀皆类此。若以意推究。恭肃便有渊静收敛之意。从乂便有宣著条畅之意。明哲便有冲和生发之意。聪谋便有裁制刚断之意。睿圣则无所不通也。如是为说。亦无不可。然仁智包含众理。贞元互相为主。局定分属。终不免牵强傅会之病。且五行传则以五事属木金火水土。先儒谓配与属不同。配者言其体。属者言其用。细看此说。自可默识。恐不必执一而论之也。上问曰。貌水言火视木听金。皆原于思土。貌思恭言思从视思明听思聪。思贯乎四事。可见寄旺四时之妙。而思是心之官。心即火。心之有思。亦火生土之理欤。
臣书九对曰。心属火脏。思属土位。土生于火而为四行之母。故思发于心而为四事之主。一理沕合。更无可疑。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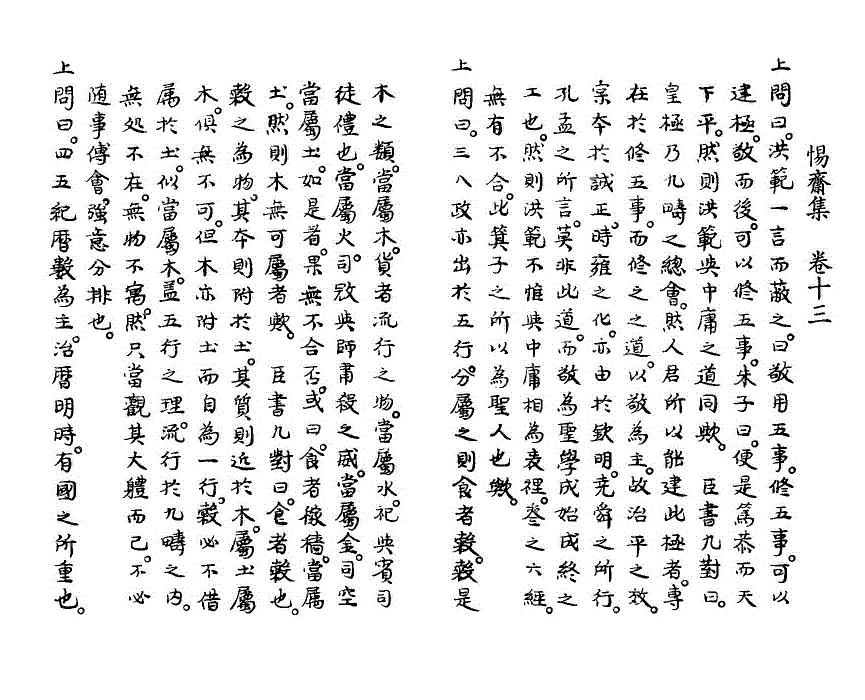 上问曰。洪范一言而蔽之。曰敬用五事。修五事。可以建极。敬而后。可以修五事。朱子曰。便是笃恭而天下平。然则洪范与中庸之道同欤。
上问曰。洪范一言而蔽之。曰敬用五事。修五事。可以建极。敬而后。可以修五事。朱子曰。便是笃恭而天下平。然则洪范与中庸之道同欤。臣书九对曰。皇极乃九畴之总会。然人君所以能建此极者。专在于修五事。而修之之道。以敬为主。故治平之效。宲本于诚正。时雍之化。亦由于钦明。尧舜之所行。孔孟之所言。莫非此道。而敬为圣学成始成终之工也。然则洪范不惟与中庸相为表里。参之六经。无有不合。此箕子之所以为圣人也欤。
上问曰。三八政亦出于五行。分属之则食者谷。谷是木之类。当属木。货者流行之物。当属水。祀与宾司徒礼也。当属火。司寇与师肃杀之威。当属金。司空当属土。如是看。果无不合否。或曰。食者稼穑。当属土。然则木无可属者欤。
臣书九对曰。食者谷也。谷之为物。其本则附于土。其质则近于木。属土属木。俱无不可。但木亦附土而自为一行。谷必不借属于土。似当属木。盖五行之理。流行于九畴之内。无处不在。无物不寓。然只当观其大体而已。不必随事傅会。强意分排也。
上问曰。四五纪历数为主。治历明时。有国之所重也。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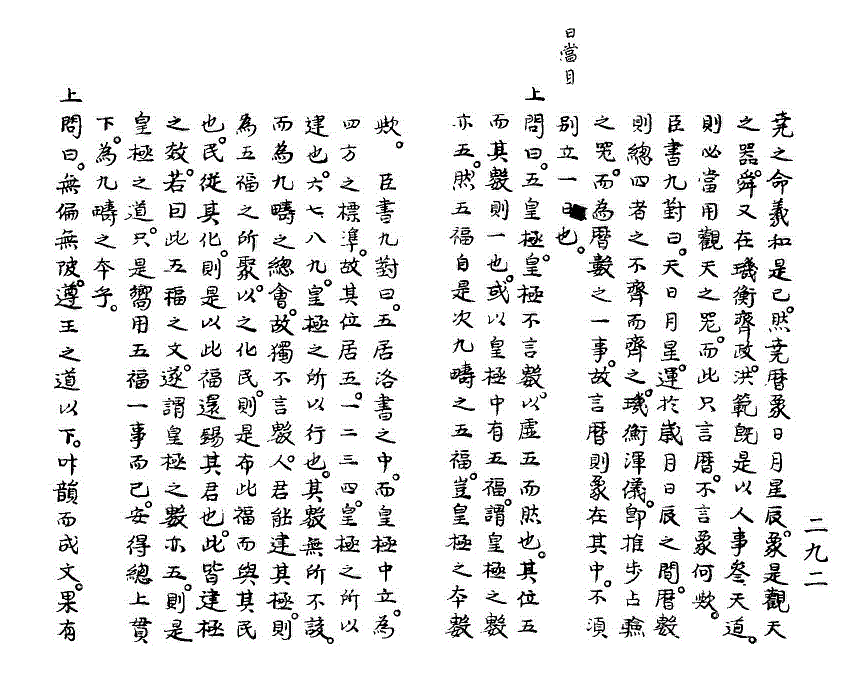 尧之命羲和是已。然尧历象日月星辰。象是观天之器。舜又在玑衡齐政。洪范既是以人事参天道。则必当用观天之器。而此只言历。不言象何欤。
尧之命羲和是已。然尧历象日月星辰。象是观天之器。舜又在玑衡齐政。洪范既是以人事参天道。则必当用观天之器。而此只言历。不言象何欤。臣书九对曰。天日月星。运于岁月日辰之间。历数则总四者之不齐而齐之。玑衡浑仪。即推步占验之器。而为历数之一事。故言历则象在其中。不须别立一目也。
上问曰。五皇极。皇极不言数。以虚五而然也。其位五而其数则一也。或以皇极中有五福。谓皇极之数亦五。然五福自是次九畴之五福。岂皇极之本数欤。
臣书九对曰。五居洛书之中。而皇极中立。为四方之标准。故其位居五。一二三四。皇极之所以建也。六七八九。皇极之所以行也。其数无所不该。而为九畴之总会。故独不言数。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以之化民。则是布此福而与其民也。民从其化。则是以此福还锡其君也。此皆建极之效。若因此五福之文。遂谓皇极之数亦五。则是皇极之道。只是向用五福一事而已。安得总上贯下。为九畴之本乎。
上问曰。无偏无陂。遵王之道以下。叶韵而成文。果有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3H 页
 诗之体。蔡氏欲使民咏歌而感发兴起者是也。陆象山在荆。罢上元醮祭。设讲座诵皇极。使民听之。亦此意。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下文皇极之敷言。是有德而有言。故民行之矣。苟不能身修五事。建极于上。以为标准。而徒以诗语。欲动民之听。不已疏乎。以此为设教之法则可。恐非化民之本。化民之本。惟在于人主一心。何以则绝偏陂之私。而成建极之治。使民归于极与。
诗之体。蔡氏欲使民咏歌而感发兴起者是也。陆象山在荆。罢上元醮祭。设讲座诵皇极。使民听之。亦此意。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下文皇极之敷言。是有德而有言。故民行之矣。苟不能身修五事。建极于上。以为标准。而徒以诗语。欲动民之听。不已疏乎。以此为设教之法则可。恐非化民之本。化民之本。惟在于人主一心。何以则绝偏陂之私。而成建极之治。使民归于极与。臣书九对曰。洪范之畴。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莫非皇极之所以建也。然大本立而达道行。夫四海之大。兆民之众。习俗之强弱不同。气质之粹驳各殊。而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操祸福予夺之权而以制其命。必也是非明好恶公然后。其所以祸福予夺之者。得乎天理之正。合乎人心之同。而贤者劝。不肖者惩。偕归于平荡正直之域。建极之治。于是乎成矣。第其所以明是非公好恶者。又在于先正其心。是故精一执中。宲为唐虞以来相传之心法也。此章之体。咏叹淫泆。读之使人感发其善心。惩创其邪思。直与九歌之劝。六诗之教。同其功用。然苟为无本而民不从。故在上者必先立其本。而身教言教。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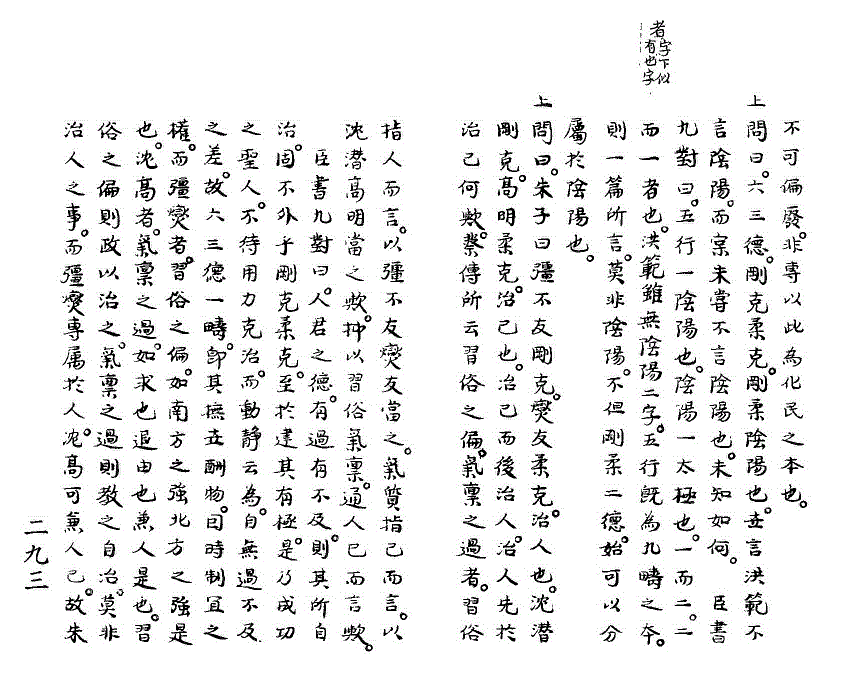 不可偏废。非专以此为化民之本也。
不可偏废。非专以此为化民之本也。上问曰。六三德。刚克柔克。刚柔阴阳也。世言洪范不言阴阳。而宲未尝不言阴阳也。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范虽无阴阳二字。五行既为九畴之本。则一篇所言。莫非阴阳。不但刚柔二德。始可以分属于阴阳也。
上问曰。朱子曰彊不友刚克。燮友柔克。治人也。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治己也。治己而后治人。治人先于治己何欤。蔡传所云习俗之偏。气禀之过者。习俗指人而言。以彊不友燮友当之。气质指己而言。以沈潜高明当之欤。抑以习俗气禀。通人己而言欤。
臣书九对曰。人君之德。有过有不及。则其所自治。固不外乎刚克柔克。至于建其有极。是乃成功之圣人。不待用力克治。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故六三德一畴。即其抚世酬物。因时制宜之权。而彊燮者。习俗之偏。如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是也。沈高者。气禀之过。如求也退由也兼人是也。习俗之偏则政以治之。气禀之过则教之自治。莫非治人之事。而彊燮专属于人。沈高可兼人己。故朱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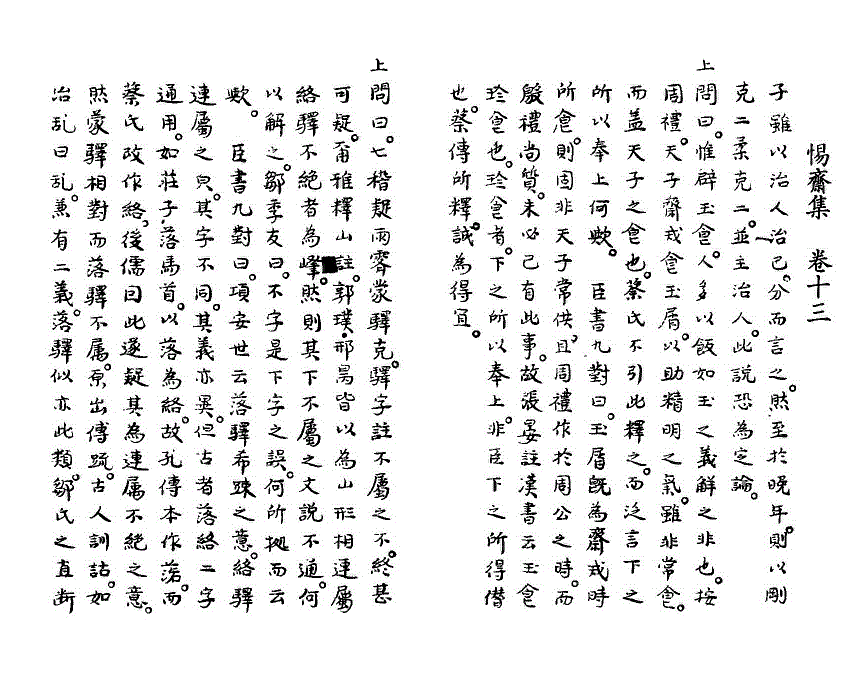 子虽以治人治己。分而言之。然至于晚年。则以刚克二柔克二。并主治人。此说恐为定论。
子虽以治人治己。分而言之。然至于晚年。则以刚克二柔克二。并主治人。此说恐为定论。上问曰。惟辟玉食。人多以饭如玉之义解之非也。按周礼。天子斋戒食玉屑。以助精明之气。虽非常食。而盖天子之食也。蔡氏不引此释之。而泛言下之所以奉上何欤。
臣书九对曰。玉屑既为斋戒时所食。则固非天子常供。且周礼作于周公之时。而殷礼尚质。未必已有此事。故张晏注汉书云玉食珍食也。珍食者。下之所以奉上。非臣下之所得僭也。蔡传所释。诚为得宜。
上问曰。七稽疑雨霁蒙驿克。驿字注不属之不。终甚可疑。尔雅释山注。郭璞,邢炳皆以为山形相连属络驿不绝者为峄。然则其下不属之文说不通。何以解之。邹季友曰。不字是下字之误。何所据而云欤。
臣书九对曰。项安世云落驿希疏之意。络驿连属之貌。其字不同。其义亦异。但古者落络二字通用。如庄子落马首。以落为络。故孔传本作落。而蔡氏改作络。后儒因此遂疑其为连属不绝之意。然蒙驿相对而落驿不属。原出傅疏。古人训诂。如治乱曰乱。兼有二义。落驿似亦此类。邹氏之直断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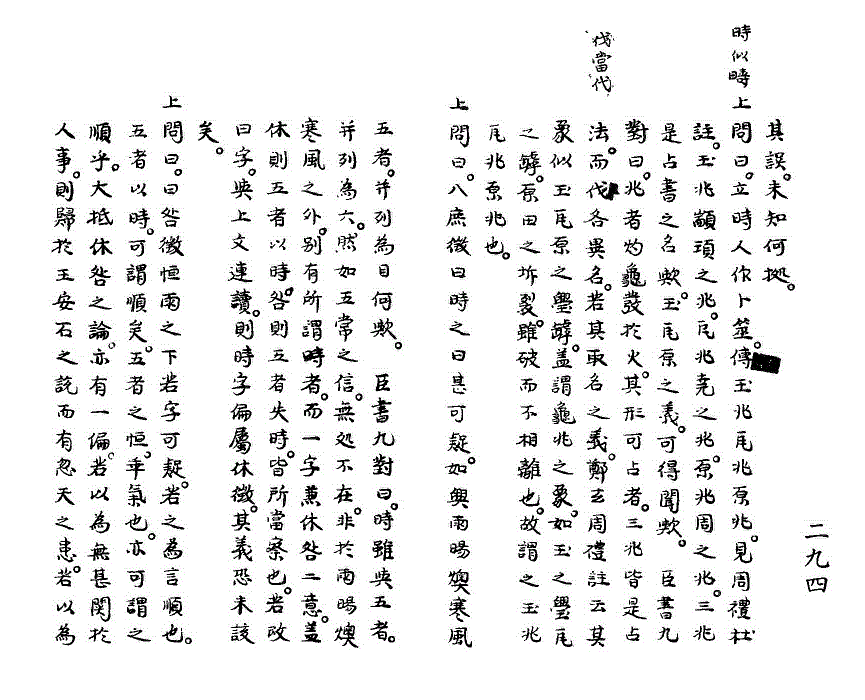 其误。未知何据。
其误。未知何据。上问曰。立时(时似畴)人作卜筮。传玉兆瓦兆原兆。见周礼杜注。玉兆颛顼之兆。瓦兆尧之兆。原兆周之兆。三兆是占书之名欤。玉瓦原之义。可得闻欤。
臣书九对曰。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三兆皆是占法。而代各异名。若其取名之义。郑玄周礼注云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盖谓龟兆之象。如玉之璺瓦之罅。原田之坼裂。虽破而不相离也。故谓之玉兆瓦兆原兆也。
上问曰。八庶徵曰时之曰甚可疑。如兴雨旸燠寒风五者。并列为目何欤。
臣书九对曰。时虽与五者。并列为六。然如五常之信。无处不在。非于雨旸燠寒风之外。别有所谓时者。而一字兼休咎二意。盖休则五者以时。咎则五者失时。皆所当察也。若改曰字。与上文连读。则时字偏属休徵。其义恐未该矣。
上问曰。曰咎徵恒雨之下若字可疑。若之为言顺也。五者以时。可谓顺矣。五者之恒。乖气也。亦可谓之顺乎。大抵休咎之论。亦有一偏。若以为无甚关于人事。则归于王安石之说而有忽天之患。若以为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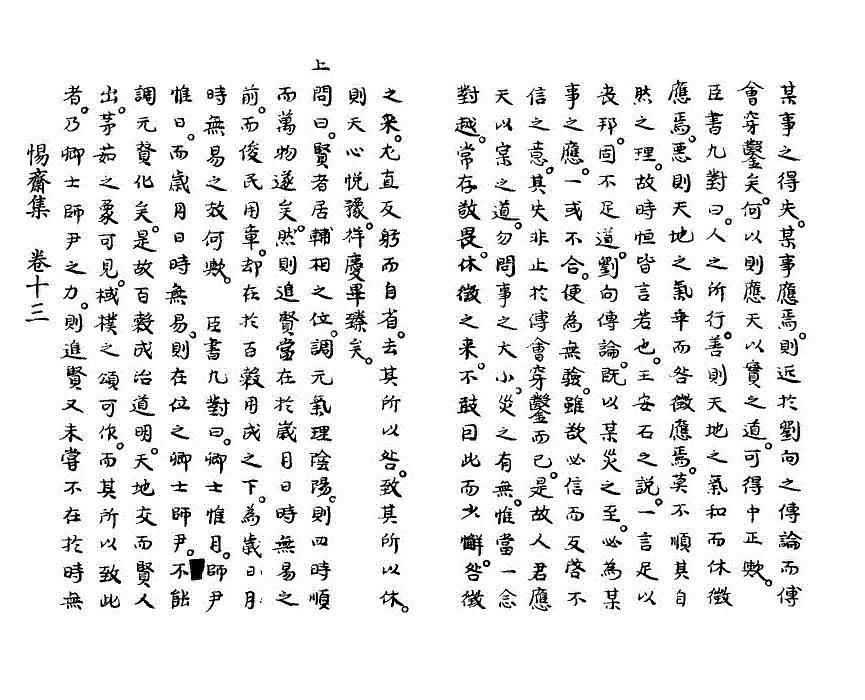 某事之得失。某事应焉。则近于刘向之传论而傅会穿凿矣。何以则应天以实之道。可得中正欤。
某事之得失。某事应焉。则近于刘向之传论而傅会穿凿矣。何以则应天以实之道。可得中正欤。臣书九对曰。人之所行。善则天地之气和而休徵应焉。恶则天地之气乖而咎徵应焉。莫不顺其自然之理。故时恒皆言若也。王安石之说。一言足以丧邦。固不足道。刘向传论。既以某灾之至。必为某事之应。一或不合。便为无验。虽欲必信而反启不信之意。其失非止于傅会穿凿而已。是故人君应天以宲之道。勿问事之大小。灾之有无。惟当一念对越。常存敬畏。休徵之来。不敢因此而少懈。咎徵之来。尤直反躬而自省。去其所以咎。致其所以休。则天心悦豫。祥庆毕臻矣。
上问曰。贤者居辅相之位。调元气理阴阳。则四时顺而万物遂矣。然则进贤当在于岁月日时无易之前。而俊民用章。却在于百谷用成之下。为岁月日时无易之效何欤。
臣书九对曰。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而岁月日时无易。则在位之卿士师尹。不能调元赞化矣。是故百谷成治道明。天地交而贤人出。茅茹之象可见。棫朴之颂可作。而其所以致此者。乃卿士师尹之力。则进贤又未尝不在于时无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5L 页
 易之前矣。
易之前矣。上问曰。庶民惟星。当在于师尹惟日之下。朱子亦云。而既不可断以错简。则惟当依本文看欤。
臣书九对曰。惟岁惟月惟日惟星。文虽似属。卿士师尹与庶民。其事各异。不可混合为说。故自岁月日。至家用不宁。总结上文。又以庶民惟星。别作一段。文义不得不尔。断非错简也。
上问曰。九五福。富则人主禄之。固可使富也。寿则人之禀气。有长短之不齐。何以使民皆寿欤。尧舜之世。民登寿域。以上古气淳俗朴。无忘生徇欲之害也。后世岂能然欤。抑气机有转移之道。而寿民之丹。自有其术欤。愿闻之。
臣书九对曰。民寿长短。虽有天定。然若其回干转移之权。专在于人主。苟能正心修身。建极于上。使天下之民。莫不从化。则一理感应。协气充满。跻斯世于春台寿域之中矣。蕫子所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焉者是也。况仁者必寿。乃理之常。民皆攸好德。则决无忘生徇欲。中绝其命之理。故曰人君造命。此乃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为治道之极功也。
上问曰。德则致福。恶则致极。而德与恶。又为一福一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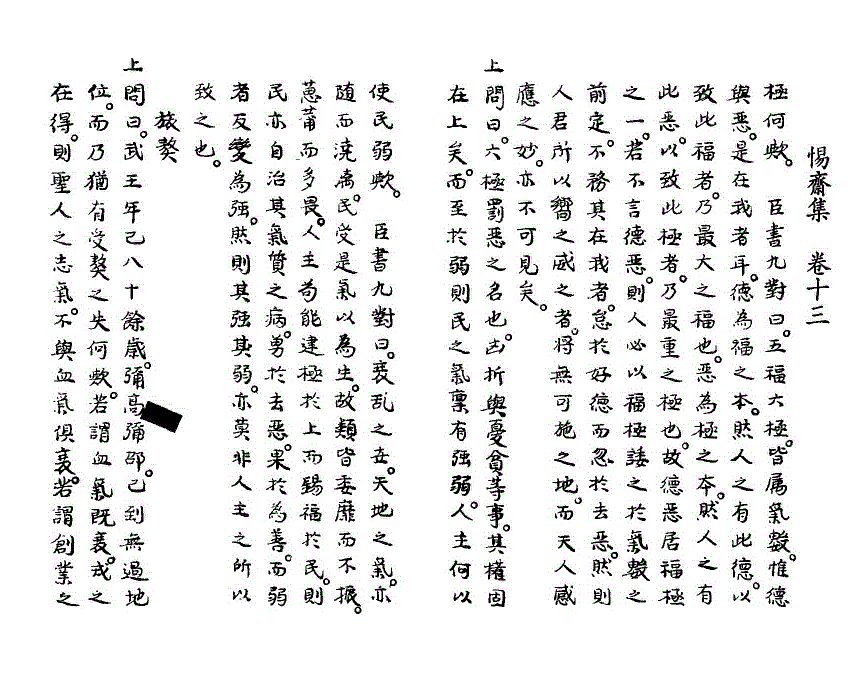 极何欤。
极何欤。臣书九对曰。五福六极。皆属气数。惟德与恶。是在我者耳。德为福之本。然人之有此德。以致此福者。乃最大之福也。恶为极之本。然人之有此恶。以致此极者。乃最重之极也。故德恶居福极之一。若不言德恶。则人必以福极诿之于气数之前定。不务其在我者。怠于好德而忽于去恶。然则人君所以向之威之者。将无可施之地。而天人感应之妙。亦不可见矣。
上问曰。六极罚恶之名也。凶折与忧贫等事。其权固在上矣。而至于弱则民之气禀有强弱。人主何以使民弱欤。
臣书九对曰。衰乱之世。天地之气。亦随而浇漓。民受是气以为生。故类皆委靡而不振。葸薾而多畏。人主苟能建极于上而锡福于民。则民亦自治其气质之病。勇于去恶。果于为善。而弱者反变为强。然则其强其弱。亦莫非人主之所以致之也。
旅獒
上问曰。武王年已八十馀岁。弥高弥卲。已到无过地位。而乃犹有受獒之失何欤。若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则圣人之志气。不与血气俱衰。若谓创业之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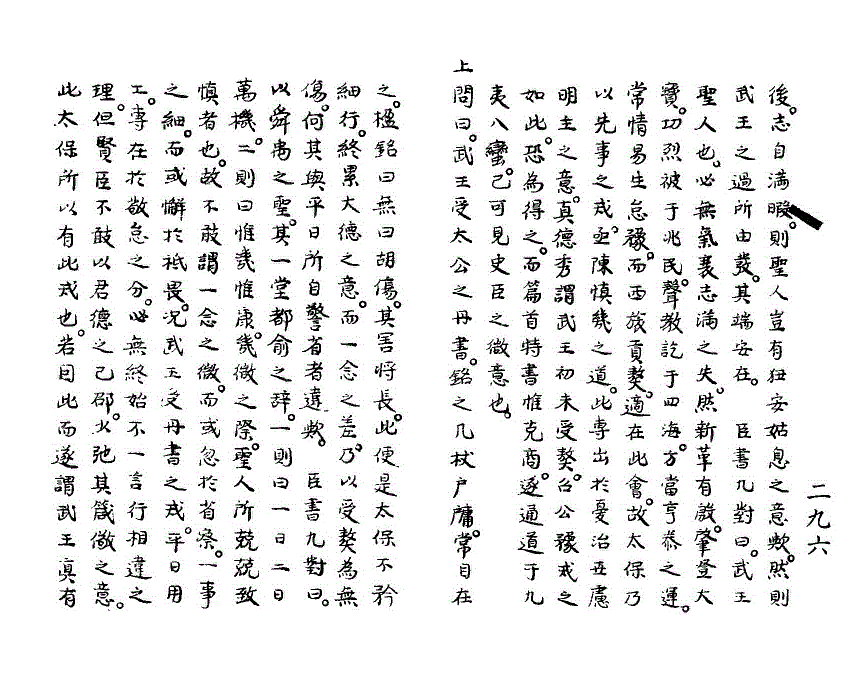 后。志自满暇。则圣人岂有狃安姑息之意欤。然则武王之过所由发。其端安在。
后。志自满暇。则圣人岂有狃安姑息之意欤。然则武王之过所由发。其端安在。臣书九对曰。武王圣人也。必无气衰志满之失。然新革有殷。肇登大宝。功烈被于兆民。声教讫于四海。方当亨泰之运。常情易生怠豫。而西旅贡獒。适在此会。故太保乃以先事之戒。亟陈慎几之道。此专出于忧治世虑明主之意。真德秀谓武王初未受獒。召公豫戒之如此。恐为得之。而篇首特书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已可见史臣之微意也。
上问曰。武王受太公之丹书。铭之几杖户
臣书九对曰。以舜禹之圣。其一堂都俞之辞。一则曰一日二日万机。二则曰惟几惟康。几微之际。圣人所兢兢致慎者也。故不敢谓一念之微。而或忽于省察。一事之细。而或懈于祗畏。况武王受丹书之戒。平日用工。专在于敬怠之分。必无终始不一言行相违之理。但贤臣不敢以君德之已卲。少弛其箴儆之意。此太保所以有此戒也。若因此而遂谓武王真有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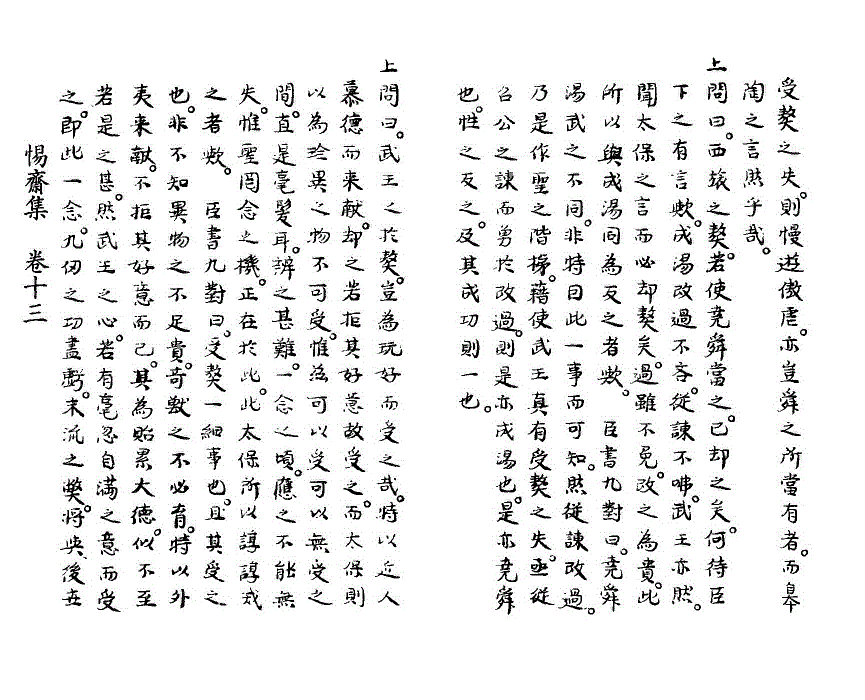 受獒之失。则慢游傲虐。亦岂舜之所当有者。而𦤎陶之言然乎哉。
受獒之失。则慢游傲虐。亦岂舜之所当有者。而𦤎陶之言然乎哉。上问曰。西旅之獒。若使尧舜当之。已却之矣。何待臣下之有言欤。成汤改过不吝。从谏不咈。武王亦然。闻太保之言而必却獒矣。过虽不免。改之为贵。此所以与成汤同为反之者欤。
臣书九对曰。尧舜汤武之不同。非特因此一事而可知。然从谏改过。乃是作圣之阶梯。藉使武王真有受獒之失。亟从召公之谏而勇于改过。则是亦成汤也。是亦尧舜也。性之反之。及其成功则一也。
上问曰。武王之于獒。岂为玩好而受之哉。特以近人慕德而来献。却之若拒其好意故受之。而太保则以为珍异之物不可受。惟玆可以受可以无受之间。直是毫发耳。辨之甚难。一念之顷。应之不能无失。惟圣罔念之机。正在于此。此太保所以谆谆戒之者欤。
臣书九对曰。受獒一细事也。且其受之也。非不知异物之不足贵。奇兽之不必育。特以外夷来献。不拒其好意而已。其为贻累大德。似不至若是之甚。然武王之心。若有毫忽自满之意而受之。即此一念。九仞之功尽亏。末流之弊。将与后世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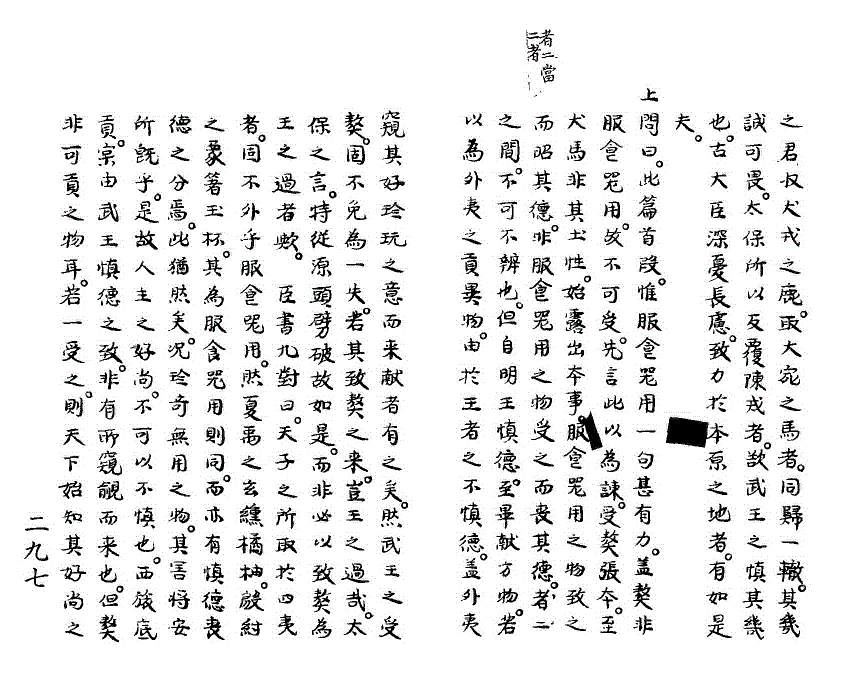 之君收犬戎之鹿。取大宛之马者。同归一辙。其几诚可畏。太保所以反覆陈戒者。欲武王之慎其几也。古大臣深忧长虑。致力于本原之地者。有如是夫。
之君收犬戎之鹿。取大宛之马者。同归一辙。其几诚可畏。太保所以反覆陈戒者。欲武王之慎其几也。古大臣深忧长虑。致力于本原之地者。有如是夫。上问曰。此篇首段。惟服食器用一句甚有力。盖獒非服食器用。故不可受。先言此以为谏。受獒张本。至犬马非其土性。始露出本事。服食器用之物致之而昭其德。非服食器用之物受之而丧其德。二者之间。不可不辨也。但自明王慎德。至毕献方物。若以为外夷之贡异物。由于王者之不慎德。盖外夷窥其好珍玩之意而来献者有之矣。然武王之受獒。固不免为一失。若其致獒之来。岂王之过哉。太保之言。特从源头劈破故如是。而非必以致獒为王之过者欤。
臣书九对曰。天子之所取于四夷者。固不外乎服食器用。然夏禹之玄纁橘柚。殷纣之象箸玉杯。其为服食器用则同。而亦有慎德丧德之分焉。此犹然矣。况珍奇无用之物。其害将安所既乎。是故人主之好尚。不可以不慎也。西旅底贡。宲由武王慎德之致。非有所窥觎而来也。但獒非可贡之物耳。若一受之。则天下始知其好尚之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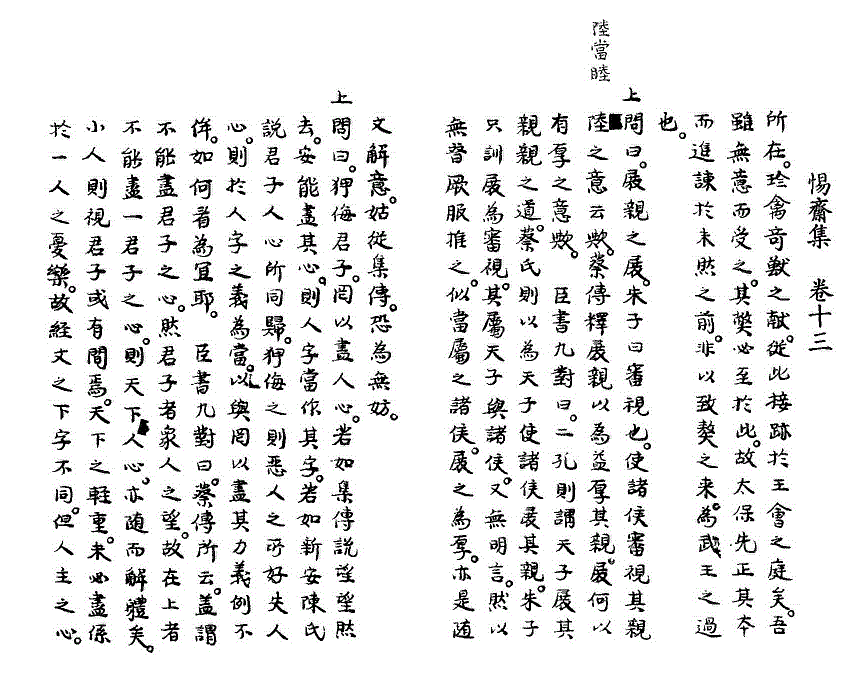 所在。珍禽奇兽之献。从此接迹于王会之庭矣。吾虽无意而受之。其弊必至于此。故太保先正其本而进谏于未然之前。非以致獒之来。为武王之过也。
所在。珍禽奇兽之献。从此接迹于王会之庭矣。吾虽无意而受之。其弊必至于此。故太保先正其本而进谏于未然之前。非以致獒之来。为武王之过也。上问曰。展亲之展。朱子曰审视也。使诸侯审视其亲睦之意云欤。蔡传释展亲以为益厚其亲。展何以有厚之意欤。
臣书九对曰。二孔则谓天子展其亲亲之道。蔡氏则以为天子使诸侯展其亲。朱子只训展为审视。其属天子与诸侯。又无明言。然以无替厥服推之。似当属之诸侯。展之为厚。亦是随文解意。姑从集传。恐为无妨。
上问曰。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若如集传说望望然去。安能尽其心。则人字当作其字。若如新安陈氏说君子人心所同归。狎侮之则恶人之所好失人心。则于人字之义为当。以与罔以尽其力义例不侔。如何看为宜耶。
臣书九对曰。蔡传所云。盖谓不能尽君子之心。然君子者众人之望。故在上者不能尽一君子之心。则天下人心。亦随而解体矣。小人则视君子或有间焉。天下之轻重。未必尽系于一人之忧乐。故经文之下字不同。但人主之心。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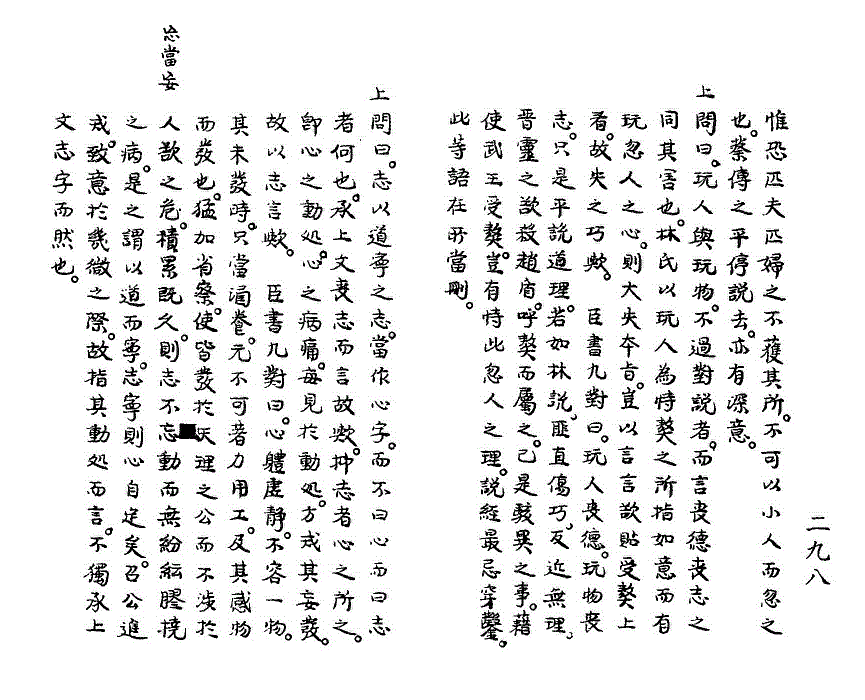 惟恐匹夫匹妇之不获其所。不可以小人而忽之也。蔡传之平停说去。亦有深意。
惟恐匹夫匹妇之不获其所。不可以小人而忽之也。蔡传之平停说去。亦有深意。上问曰。玩人与玩物。不过对说者。而言丧德丧志之同其害也。林氏以玩人为恃獒之所指如意而有玩忽人之心。则大失本旨。岂以言言欲贴受獒上看。故失之巧欤。
臣书九对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只是平说道理。若如林说。匪直伤巧。反近无理。晋灵之欲杀赵盾。呼獒而属之。已是骇异之事。藉使武王受獒。岂有恃此忽人之理。说经最忌穿凿。此等语在所当删。
上问曰。志以道宁之志。当作心字。而不曰心而曰志者何也。承上文丧志而言故欤。抑志者心之所之。即心之动处。心之病痛。每见于动处。方戒其妄发。故以志言欤。
臣书九对曰。心体虚静。不容一物。其未发时。只当涵养。元不可著力用工。及其感物而发也。猛加省察。使皆发于天理之公而不涉于人欲之危。积累既久。则志不妄动而无纷纭胶挠之病。是之谓以道而宁。志宁则心自定矣。召公进戒。致意于几微之际。故指其动处而言。不独承上文志字而然也。
惕斋集卷之十三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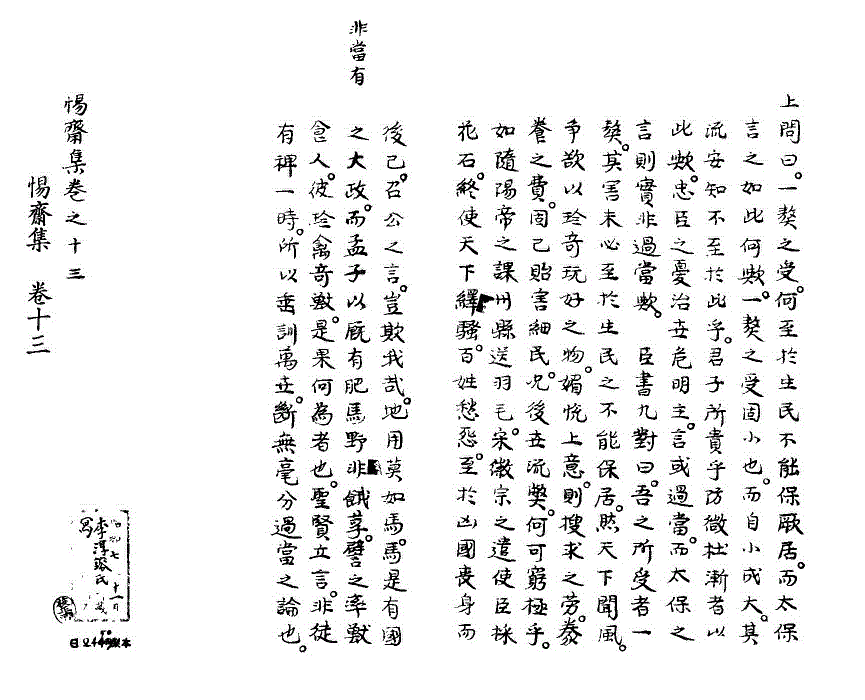 上问曰。一獒之受。何至于生民不能保厥居。而太保言之如此何欤。一獒之受固小也。而自小成大。其流安知不至于此乎。君子所贵乎防微杜渐者以此欤。忠臣之忧治世危明主。言或过当。而太保之言则实非过当欤。
上问曰。一獒之受。何至于生民不能保厥居。而太保言之如此何欤。一獒之受固小也。而自小成大。其流安知不至于此乎。君子所贵乎防微杜渐者以此欤。忠臣之忧治世危明主。言或过当。而太保之言则实非过当欤。臣书九对曰。吾之所受者一獒。其害未必至于生民之不能保居。然天下闻风。争欲以珍奇玩好之物。媚悦上意。则搜求之劳。豢养之费。固已贻害细民。况后世流弊。何可穷极乎。如随炀帝之课州县送羽毛。宋徽宗之遣使臣采花石。终使天下绎骚。百姓愁怨。至于凶国丧身而后已。召公之言。岂欺我哉。地用莫如马。马是有国之大政。而孟子以厩有肥马野有饿莩。譬之率兽食人。彼珍禽奇兽。是果何为者也。圣贤立言。非徒有裨一时。所以垂训万世。断无毫分过当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