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惕斋集卷之十一
尚书讲义[二]
尚书讲义[二]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38H 页
 禹贡
禹贡上问曰。朱子曰禹贡所记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晓。其不可晓者。果在何处耶。断之以不可晓。则终难强说耶。又曰禹贡地理。不可大段用心。然则薛士龙地经工夫。非学者急务欤。然天下地势。考验得来。亦学者分内事。则六合之外。固当存而不论。九州之内疆界。其不可论辨欤。
臣书九对曰。禹贡一书。宲为后世舆志之宗。而地名之沿革不同。水道之迁徙无常。以今视古。势多龃龉。考论辨證。是亦读书者之所不可忽。如毛晃,程大昌之专门著书。用心非不精勤。或不免牵合傅会。且比切问近思之学。自有缓急。故朱子之言如此。然若其耳目所及如彭蠡洞庭之类。朱子亦未尝不辨也。
上问曰。世言禹治水肯綮。在于凿龙门手段。而朱子以为不深信何也。既不深信。而又曰自积石至龙门。禹费工夫最多者何欤。
臣书九对曰。不杀下流。先凿龙门。水道壅塞。决难成功。故以为未敢深信。河到龙门。势益奔放。凿石通水。功力必钜。故以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38L 页
 为费工最多。朱子两说。自不相妨。
为费工最多。朱子两说。自不相妨。上问曰。朱子曰南方诸水。禹不曾亲见。遣其官属往视。具图说以归。故所记载不齐整耳。禹之八年居外。手足胼胝。而犹未能一一亲自为之。其于区分山川。亦有疏略未尽者欤。
臣书九对曰。洪水之患。惟河为甚。河功既成。则馀水虽不大费疏凿。自当安流。遣属往莅。理或似然。且朱子生长南方。江处以北。未尝亲历。其所致疑。尤在于耳目所及之处。故论辨如此。然此亦推究事势而言。禹迹之及与不及。既无明据。不敢臆断。
上问曰。朱子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水河水混同江是也。混同江不见于禹贡何也。禹贡中山水多有名同者。梁山有二。岐山有二。碣石有二。漳水有二。沮水有二。沂水有三。沱水有三。漆水有二。若此类固当按啚考志而别之。至于古今地名之不同。如九江为洞庭之类。终不可的定欤。且百千年后。陵谷变迁。沧桑幻改。莫寻其处。如九河之类。当以阙疑之例处之欤。
臣书九对曰。此篇所记。皆是禹所经理之地。馀不备书。冀州东北。无所施功。故并皆略之。况混同江遥在夷貊之域。不见于禹贡。固其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39H 页
 宜也。九江汉儒以彭蠡当之。朱子辨其误曰即今洞庭是也。或者又并诋二说。只云江水分派。正当在荆州之东岳州之北。亦不明言其为某水。莫能归一。然通儒皆主洞庭之说。则终当以朱子为正。九河所在。既难的知。只当参考先儒之说。传信阙疑而已。
宜也。九江汉儒以彭蠡当之。朱子辨其误曰即今洞庭是也。或者又并诋二说。只云江水分派。正当在荆州之东岳州之北。亦不明言其为某水。莫能归一。然通儒皆主洞庭之说。则终当以朱子为正。九河所在。既难的知。只当参考先儒之说。传信阙疑而已。上问曰。禹贡书法。虽大山大水。不费疏凿则不书。荒近则略之矣。山水之见于禹贡者四十有五。四十五之外。某山某水之不入。当为几何。皆可历指而言欤。
臣书九对曰。禹贡一篇。天下山川脉络形势。大纲可见。然周礼职方氏所记九州之山泽川没。皆是一方之大山大水。尚多阙略。则馀外流峙之不载者。有难历指而悉数矣。
上问曰。随山以下文导岍及岐注。此下随山也之文观之。随山即导山也。随山是治水三纲领之一。则导水之意。亦包在于随山之中欤。
臣书九对曰。导山本为治水言。随山则通水自在其中。故善谈舆地者。欲知水道往来。先审山势向背。而千里之外。瞭如指掌。此亦一验。
上问曰。冀州以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观之。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39L 页
 自尧始都之也。帝王定都。必以地利可居。冀州三面距河。最易被水害。则尧之必都此何也。冀州不言疆界。别于诸州之例也。或言冀字从北从异。以其居北。而帝都异于诸州也。以此推之。诸州之名称。皆有其义之可言欤。
自尧始都之也。帝王定都。必以地利可居。冀州三面距河。最易被水害。则尧之必都此何也。冀州不言疆界。别于诸州之例也。或言冀字从北从异。以其居北。而帝都异于诸州也。以此推之。诸州之名称。皆有其义之可言欤。臣书九对曰。考之传记。神农都陈。颛顼都帝丘。高辛都亳。皆今河南地。而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盖冀都背负太行。地势最高。洪水为患。亦由下流壅塞。水势汎滥而然。若非河南之湫下。为水所注之地。虽以后世史传观之。河之冲决。常在河南而不在山西。则尧之定都。亦可谓得地利矣。说文。冀北方州。以北异声字。属谐声非会意。谓异于诸州者。恐近傅会。至于诸州名义。李巡,刘熙辈虽有豫舒壅塞荆警兖信之说。终不为通儒之所取也。
上问曰。既修太原注曰。修因鲧之功而修之也。鲧虽绩用不成。而亦有些少功绩。如朱子说耶。必言修者。不以其恶而掩其功能。史氏之笔法。亦可见欤。此独言修而他不言者。鲧之功。止于太原岳阳耶。
臣书九对曰。鲧之治水。不先疏下流。以杀河势。只从近尧都处。极意崇防。所以绩用不成。然用力既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0H 页
 多。亦颇有遗迹可因禹乃自兖为始。专事疏凿。河流既定。太原一带。只修鲧旧绩。自可奏功。此禹之行其所无事。而史氏书之曰修鲧迹。因禹而并著矣。此独言修者。非鲧于馀州皆无事也。但冀州则最费工夫。禹亦资此而成功故耳。
多。亦颇有遗迹可因禹乃自兖为始。专事疏凿。河流既定。太原一带。只修鲧旧绩。自可奏功。此禹之行其所无事。而史氏书之曰修鲧迹。因禹而并著矣。此独言修者。非鲧于馀州皆无事也。但冀州则最费工夫。禹亦资此而成功故耳。上问曰。衡漳郦道元曰。衡水合清漳。是二水也。孔氏曰。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是一水也。当从何说欤。
臣书九对曰。孔传谓漳水横流入河者。盖二漳合流。同入于河。故以河为经流。而总名二水曰衡漳。王肃则谓衡漳二水名。而以浊漳为衡。清漳为漳。水经注亦同此说。而近世之论。又以清漳为衡漳。未详孰是。然东汉以后。河日东徙。漳不入河而自达于海。故桑钦之经。郦氏之注。已异于孔传。是皆各据其时所见而言尔。
上问曰。兖州九河既道。九河先儒说皆未的确。毕竟以程氏沦入于海之说为定耶。孔氏曰九河在此州界平原北。何据而知之。其有闻见于未沦入海之前欤。
臣书九对曰。九河之名。堇见尔雅。而故道迁徙。汉唐诸儒访求古迹。卒无明据。蔡传遂从程大昌说以为沦入海中。因以碣石为證。然近世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0L 页
 之论。以今天津直沽为逆河旧道。则九河要不出其左右。或谓自当在德州以上河间数百里之地者。似为可信。而与孔传所云。不甚径庭也。
之论。以今天津直沽为逆河旧道。则九河要不出其左右。或谓自当在德州以上河间数百里之地者。似为可信。而与孔传所云。不甚径庭也。上问曰。厥赋贞。不曰下下而曰贞。语意极好。王者取于民而有制。过则非正。无逸篇惟正之供之正。实本于此。若使后世人记之。必曰厥赋下下矣。上古之文。下字精妙如此。虞夏之时。在史官之列者。果皆圣人之徒欤。
臣书九对曰。兖赋虽薄。谓之下下。则是曰薄乎云尔。且谓之贞。则便有以薄为正之义。不惟史笔精妙。蔡传所释。深得经旨。盖贞之训正一也。孔安国谓州与赋皆第九正相当。苏轼谓田与赋皆第六正相当。蔡氏从孔传为赋九等。而独发明微意如此。其为有功于后人大矣。
上问曰。十有三载乃同。有三说。蔡传曰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盖言今则为最下。作治之后。方可比于他州。朱子谓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则此州水平。其后他州五年。王氏谓水患未尽去。则赋难定其等。故十三载。始较所收而定其赋之下下。三说中何者为正义耶。
臣书九对曰。九州定赋。当在八年治水之馀。而朱子说。恐伤于急。王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1H 页
 炎说。恐伤于缓。盖水患虽平。作治十三载之间。始薄其税。稍俟人力既齐。地利尽辟然后。始为均等定赋者。轻重缓急。俱得其中。此等处只从蔡传为宜。
炎说。恐伤于缓。盖水患虽平。作治十三载之间。始薄其税。稍俟人力既齐。地利尽辟然后。始为均等定赋者。轻重缓急。俱得其中。此等处只从蔡传为宜。上问曰。青州莱夷作牧。以畜牧为生。而无贡马之事何欤。地用莫如马。而马贡不见于九州何欤。
臣书九对曰。周官兵制。以赋出马。唐虞之际。虽未可详。井牧沟洫。维禹所甸。则其时法度。想亦如此。不必别作一贡。且左氏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冀是帝都。不献贡篚。马贡之不见。抑由斯欤。
上问曰。徐州夏翟注曰。雉具五色。周礼染人之职。秋染夏。郑氏曰。染夏者染五色。夏之为五色。其义可得闻欤。夏大也。色之具五色。为色之最大者故云耶。夏季土。土之数为五。故取之欤。
臣书九对曰。周礼染人注。郑司农云夏大也。秋乃大染。后郑不从以夏谓五色。而引夏翟为證。是五色之谓夏。亦取翟羽之备五色。更无异义。内司服。王后六服。有褕翟阙翟。孔疏以五行相生之序。分配其色。然若谓土为五数。寄位于夏。故以夏为五色之总名。则恐近傅会。未敢强解。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1L 页
 上问曰。杨州小注。武夷熊氏曰。画江淮而保障。可以偏伯。欲以规恢中原。奄有四海。则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此其故何哉。抑以南方风气柔弱而然欤。
上问曰。杨州小注。武夷熊氏曰。画江淮而保障。可以偏伯。欲以规恢中原。奄有四海。则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此其故何哉。抑以南方风气柔弱而然欤。臣书九对曰。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是故得众则一旅之师。可以中兴。失众则四塞之险。不能自强。况苟怀偏安。不恢大略。并与其地利而失之者乎。且江淮保障。亦有其道。拒淮而守则犹足以堇保一方。画江为限则其势必亡。盖以长江舟楫。与敌人共之故耳。晋宋之不竞。皆由于此。熊禾之论。抑亦有感而发也。若直断以风气之强弱。则汉高祖及 皇明太祖高皇帝始起于淮泗之间。而终能席捲天下。统一寰海。恐不可以一槩论也。
上问曰。此曰三江。集传以松江娄江东江释之。盖用庾仲初吴都赋注语。而又以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證之。又按东坡说。以中江北江南江释之。朱子不许之。蔡氏之以庾赋断之者。岂因朱子不许苏说而然耶。颜师古以中江南江北江为三江。郭景纯以岷江浙江松江为三江。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王介甫以义兴毗江(毗江即毗陵)吴县三派为三江。中原之人论说犹多端。况东国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2H 页
 人不识山川道里。岂可轻议诸说之是非。而抑有一说可辨者。朱子以东坡之不曾亲见东南水势。只将意想硬定非之。然则当就惯见道里者之说断之。按水经曰。南江东北为长渎历河口东南。注于具区。谓之五湖。东则松江出焉。江水奇分为三江口云云。以此水经说的定。未知如何耶。尝见郦道元说。亦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云者。此亦别为三江云云。以郦说推之。庾赋及春秋所谓三江口。决知非同一地名。未知如何耶。
人不识山川道里。岂可轻议诸说之是非。而抑有一说可辨者。朱子以东坡之不曾亲见东南水势。只将意想硬定非之。然则当就惯见道里者之说断之。按水经曰。南江东北为长渎历河口东南。注于具区。谓之五湖。东则松江出焉。江水奇分为三江口云云。以此水经说的定。未知如何耶。尝见郦道元说。亦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云者。此亦别为三江云云。以郦说推之。庾赋及春秋所谓三江口。决知非同一地名。未知如何耶。臣书九对曰。三江之名。杂出经传。古今注疏家人殊其说。谓自彭蠡江分为三江而入震泽者。孔安国也。谓吴县南一水为南江。芜湖西一水为中江。毗陵北一水为北江者。班固也。谓左合汉而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为中江者。郑玄也。谓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者。韦昭也。谓岷江浙江松江者。郭璞也。谓松江娄江东江者。顾夷庾仲初张守节也。而蔡氏集传。亦从是说。然王安石主班固。苏轼主郑玄。至于近世。归有光顾炎武从郭璞。纷纭聚讼。不能归一。桑钦水经。疑若可信。然郦道元注。亦引庾仲初吴都赋注。以吴越春秋之三江口。别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2L 页
 作一地。则水经(水经下似有与字)蔡传所指无异。后儒既攻蔡传之误。而以郑玄说为确不可易。则水经所载。亦难偏信。舆地之学。大有关于读书考古。然如臣謏浅。虽在我东耳目之所及。如三韩四郡之分界。浿水洌水之定在何地。尚所疑眩。又何敢捃拾陈言。硬定古人未决之疑也哉。
作一地。则水经(水经下似有与字)蔡传所指无异。后儒既攻蔡传之误。而以郑玄说为确不可易。则水经所载。亦难偏信。舆地之学。大有关于读书考古。然如臣謏浅。虽在我东耳目之所及。如三韩四郡之分界。浿水洌水之定在何地。尚所疑眩。又何敢捃拾陈言。硬定古人未决之疑也哉。上问曰。厥贡惟金三品。左传曰贡金九牧。而此篇则贡金惟见于扬荆二州何也。左传所云。非常贡而特以一时铸鼎之事而然欤。
臣书九对曰。九州莫不产金。惟扬荆二州。其品最美。故岁作常贡。馀州特贡于铸鼎之时。盖九鼎所以象九州。故各收其土之产。以作天下之重器也。
上问曰。厥包橘柚锡贡。张氏曰必锡命乃贡者。供祭祀燕宾客则诏之。宾客固是不时之事。祭祀自是岁事。亦有定时。且国之大事在祀。何不划为定式。而必临时诏之耶。若临时诏之。则扬之距帝都道里稍远。其能无促迫难及之患耶。
臣书九对曰。祭祀之羞。具有常品。周礼笾人所掌四笾之实。不过枣栗桃乾䕩榛宲菱芡之属而已。橘柚元非常品。且其色味易变。不可定作恒贡。以贻劳害。特以殊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3H 页
 方珍羞。有时锡命而荐之。亦必先时诏告。量宜进献。岂有慢令致期之患哉。
方珍羞。有时锡命而荐之。亦必先时诏告。量宜进献。岂有慢令致期之患哉。上问曰。荆州三邦底贡厥名注曰。致贡箘簬楛之有名者。凡物产之贡。多以有名称。虽以此州言之。杶栝柏皆水之有名者。菁茅亦有名者。而独于箘簬楛。以有名者言之何也。
臣书九对曰。诸州所贡。莫非土产之美者。惟箘簬楛。在此州之贡。最有名称。考工记所云荆之干妢胡之笴是也。张九成曰。厥名犹言尤美也。其说得之。
上问曰。豫州小注。朱子曰周公以土圭测天地之中。豫州为中。而南北东西际天。各远许多。至于北远而南近。则地形有偏耳。所谓地不满东南也。地之不满东南何理欤。天又不足西北。天地之大而犹有不足何欤。理无穷而气有穷。故形体有限而然欤。然则亦一物。信如邵子说欤。
臣书九对曰。郑玄以颖川阳城为地中。阳城即豫州之属也。然此特指中国之四方而言。若以天地之全体论之。中国已在北极之西赤道之北。而西北多陆。东南多水。故观今舟车所至。西北则大荒绝域。番夷杂种。壤土相连。无有不届。东南则大海隔断。自古以来。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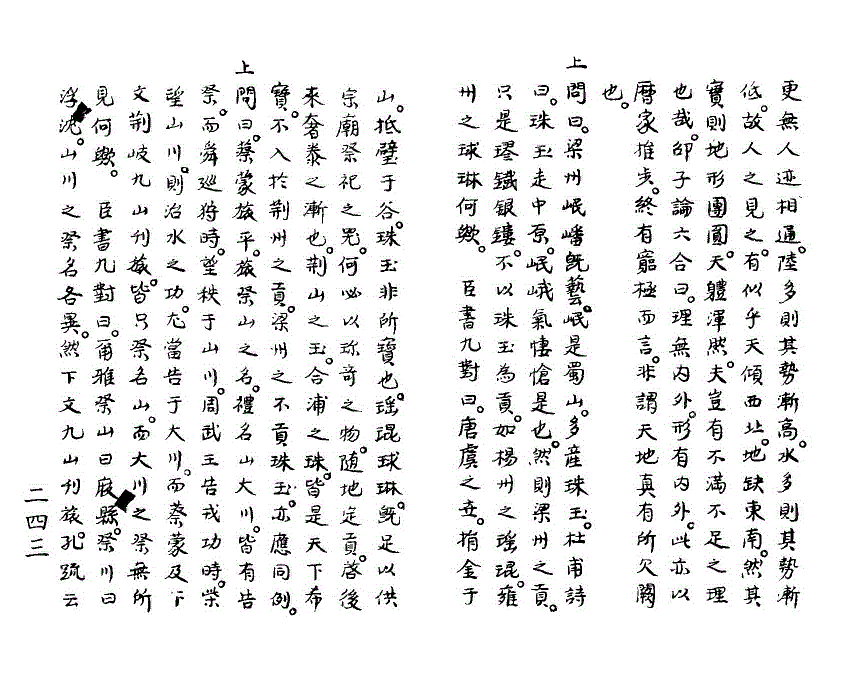 更无人迹相通。陆多则其势渐高。水多则其势渐低。故人之见之。有似乎天倾西北。地缺东南。然其实则地形团圆。天体浑然。夫岂有不满不足之理也哉。邵子论六合曰。理无内外。形有内外。此亦以历家推步。终有穷极而言。非谓天地真有所欠阙也。
更无人迹相通。陆多则其势渐高。水多则其势渐低。故人之见之。有似乎天倾西北。地缺东南。然其实则地形团圆。天体浑然。夫岂有不满不足之理也哉。邵子论六合曰。理无内外。形有内外。此亦以历家推步。终有穷极而言。非谓天地真有所欠阙也。上问曰。梁州岷嶓既艺。岷是蜀山。多产珠玉。杜甫诗曰。珠玉走中原。岷峨气悽怆是也。然则梁州之贡。只是璆铁银镂。不以珠玉为贡。如杨州之瑶琨。雍州之球琳何欤。
臣书九对曰。唐虞之世。捐金于山。抵璧于谷。珠玉非所宝也。瑶琨球琳。既足以供宗庙祭祀之器。何必以珍奇之物。随地定贡。启后来奢泰之渐也。荆山之玉。合浦之珠。皆是天下希宝。不入于荆州之贡。梁州之不贡珠玉。亦应同例。
上问曰。蔡蒙旅平。旅祭山之名。礼名山大川。皆有告祭。而舜巡狩时。望秩于山川。周武王告戎功时。柴望山川。则治水之功。尤当告于大川。而蔡蒙及下文荆岐九山刊旅。皆只祭名山。而大川之祭无所见何欤。
臣书九对曰。尔雅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山川之祭名各异。然下文九山刊旅。孔疏云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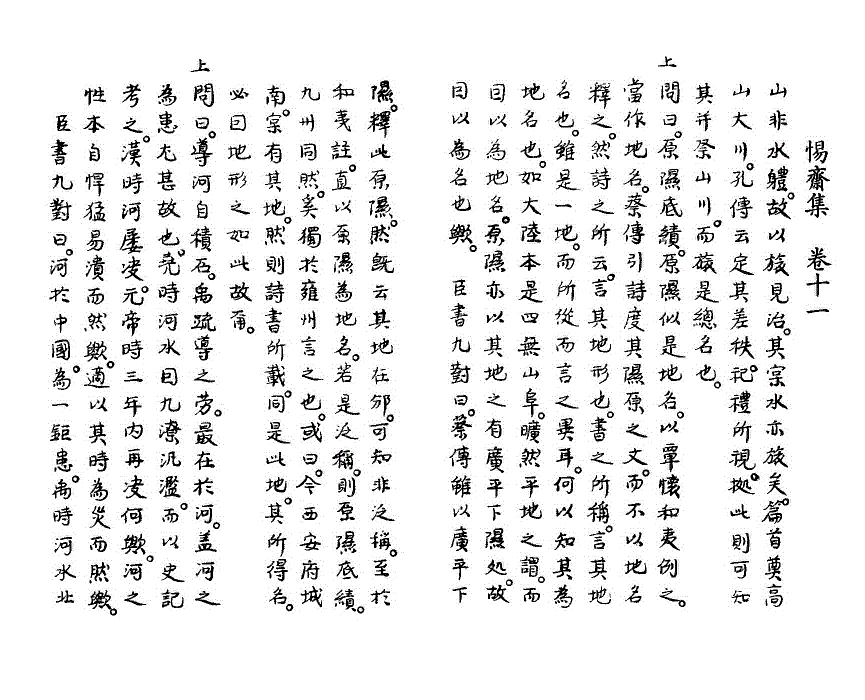 山非水体。故以旅见治。其宲水亦旅矣。篇首奠高山大川。孔传云定其差秩。祀礼所视。据此则可知其并祭山川。而旅是总名也。
山非水体。故以旅见治。其宲水亦旅矣。篇首奠高山大川。孔传云定其差秩。祀礼所视。据此则可知其并祭山川。而旅是总名也。上问曰。原隰底绩。原隰似是地名。以覃怀和夷例之。当作地名。蔡传引诗度其隰原之文。而不以地名释之。然诗之所云。言其地形也。书之所称。言其地名也。虽是一地。而所从而言之异耳。何以知其为地名也。如大陆本是四无山阜。旷然平地之谓。而因以为地名。原隰亦以其地之有广平下隰处。故因以为名也欤。
臣书九对曰。蔡传虽以广平下隰。释此原隰。然既云其地在邠。可知非泛称。至于和夷注。直以原隰为地名。若是泛称。则原隰底绩。九州同然。奚独于雍州言之也。或曰。今西安府城南。宲有其地。然则诗书所载。同是此地。其所得名。必因地形之如此故尔。
上问曰。导河自积石。禹疏导之劳。最在于河。盖河之为患尤甚故也。尧时河水因九潦汎滥。而以史记考之。汉时河屡决。元帝时三年内再决何欤。河之性本自悍猛易溃而然欤。适以其时为灾而然欤。
臣书九对曰。河于中国。为一钜患。禹时河水北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4L 页
 流入海。故九河旧道。皆在兖冀之境。周定王时。河徙砱砾。汉亦屡决。然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其患尚鲜。宋熙宁中。始分趍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元之际。北流绝全河。南流合淮入于海。青徐之间。受害尤甚。水之就下。固其势也。亦由河性悍猛。沙泥淤塞。易于横溢故尔。治河之论。惟以汉贾让为善。明都燕京。开运河。岁漕江浙之粟。故治河务者总理漕政。其有关民国。尤非前世之比矣。
流入海。故九河旧道。皆在兖冀之境。周定王时。河徙砱砾。汉亦屡决。然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其患尚鲜。宋熙宁中。始分趍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元之际。北流绝全河。南流合淮入于海。青徐之间。受害尤甚。水之就下。固其势也。亦由河性悍猛。沙泥淤塞。易于横溢故尔。治河之论。惟以汉贾让为善。明都燕京。开运河。岁漕江浙之粟。故治河务者总理漕政。其有关民国。尤非前世之比矣。上问曰。北过洚水。此水与总称之洪水名同。亦以其洪流而然欤。
臣书九对曰。水经注云郑注尚书北过洚水。洚下江反。声转为共。今河北共山共水出焉。所谓洚水也。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洚故改为共耳。说文。洚字亦不言水名。故唐石经及宋元旧本字皆作降。经文以水。乃俗本之误。非因洪水而独得此名也。
上问曰。东为北江入于海。郑渔仲欲以此为衍文何也。朱子以为北江不知所在。蔡传亦曰未详。以其如是也。故郑欲作衍文看耶。
臣书九对曰。朱子彭蠡辨。取郑樵说。谓经文东汇以下十三字为衍文。盖刱此说者樵也。当从阙疑之例。而吴澄作书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5H 页
 纂言直加移改则恐过矣。水道之湮废迁徙。古今悬殊。何可以不合己见。径断经文之误也。
纂言直加移改则恐过矣。水道之湮废迁徙。古今悬殊。何可以不合己见。径断经文之误也。上问曰。夫氏族之别。或以谥或以序或以土。宣文懿武。以谥为姓也。孟仲叔季。以序为姓也。鲁卫凡胙。以土为姓也。此言锡土姓。既锡土。又锡姓者何欤。锡土则自可为姓也。必锡之以姓者。亦有意义之可言欤。
臣书九对曰。锡土锡姓。本是二事。左传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土是锡土也。命之氏是锡姓也。然既胙土而又赐姓者。必于有功德之人。故史记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天子之子。必当分封。而尚有不得姓者。则其馀可推而知也。天下非一人所独理。尧之初载。亦岂无分茅胙土之人。而赐姓命氏。犹或未遑。及夫洪水既平之后。始乃众建诸侯。遍举阙典。他人姑无论。即禹亦至此而方得受姓。周语(周语似是国语)云帝嘉禹德。赐姓曰姒氏。曰有夏是也。故史氏谨记之如此。盖古者姓氏之辨甚明。天子锡土姓。诸侯位卑。虽不得赐姓。亦能命氏分族。或以字或以谥。或以官或以居。试以鲁之三桓言之。姬其姓也。孟孙叔孙季孙其氏也。子服南宫叔仲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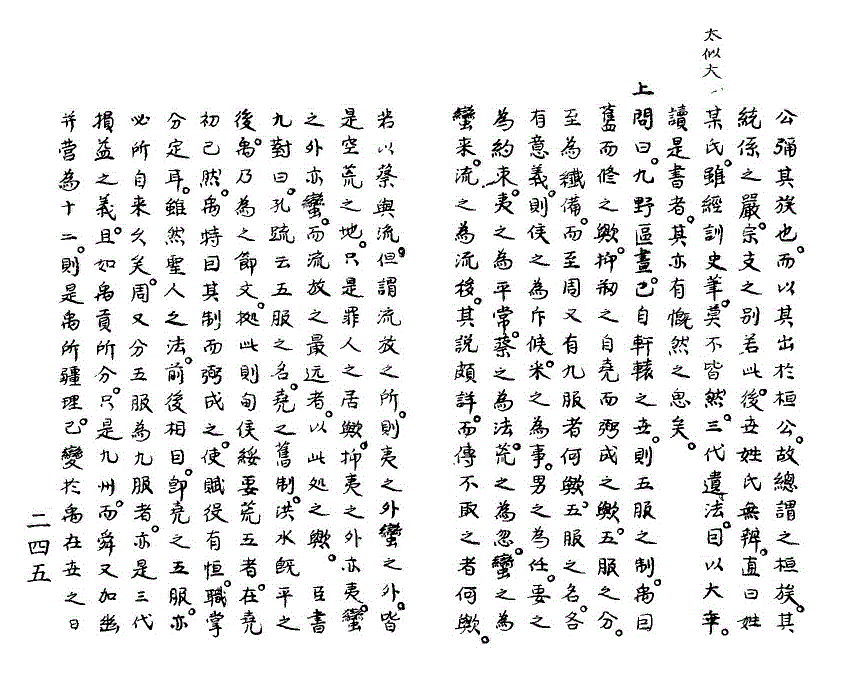 公弥其族也。而以其出于桓公。故总谓之桓族。其统系之严。宗支之别若此。后世姓氏无辨。直曰姓某氏。虽经训史笔。莫不皆然。三代遗法。因以太(太似大)乖。读是书者。其亦有慨然之思矣。
公弥其族也。而以其出于桓公。故总谓之桓族。其统系之严。宗支之别若此。后世姓氏无辨。直曰姓某氏。虽经训史笔。莫不皆然。三代遗法。因以太(太似大)乖。读是书者。其亦有慨然之思矣。上问曰。九野区画。已自轩辕之世。则五服之制。禹因旧而修之欤。抑刱之自尧而弼成之欤。五服之分。至为纤备。而至周又有九服者何欤。五服之名。各有意义。则侯之为斥候。采之为事。男之为任。要之为约束。夷之为平常。蔡之为法。荒之为忽。蛮之为蛮来。流之为流移。其说颇详。而传不取之者何欤。若以蔡与流。但谓流放之所。则夷之外蛮之外。皆是空荒之地。只是罪人之居欤。抑夷之外亦夷。蛮之外亦蛮。而流放之最远者。以此处之欤。
臣书九对曰。孔疏云五服之名。尧之旧制。洪水既平之后。禹乃为之节文。据此则甸侯绥要荒五者。在尧初已然。禹特因其制而弼成之。使赋役有恒。职掌分定耳。虽然圣人之法。前后相因。即尧之五服。亦必所自来久矣。周又分五服为九服者。亦是三代损益之义。且如禹贡所分。只是九州。而舜又加幽并营为十二。则是禹所疆理。已变于禹在世之日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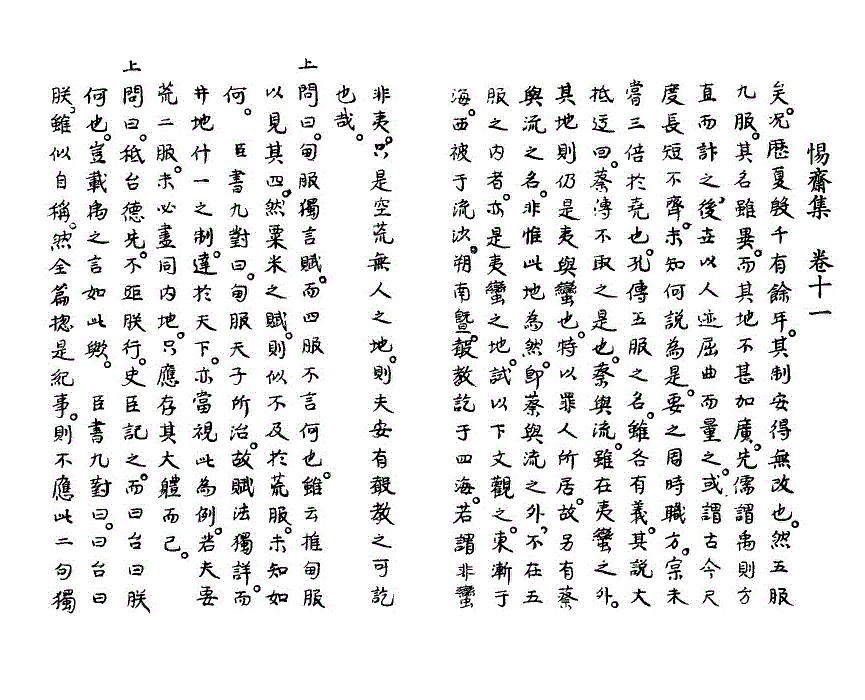 矣。况历夏殷千有馀年。其制安得无改也。然五服九服。其名虽异。而其地不甚加广。先儒谓禹则方直而计之。后世以人迹屈曲而量之。或谓古今尺度长短不齐。未知何说为是。要之周时职方。宲未尝三倍于尧也。孔传五服之名。虽各有义。其说大抵迂回。蔡传不取之是也。蔡与流。虽在夷蛮之外。其地则仍是夷与蛮也。特以罪人所居。故另有蔡与流之名。非惟此地为然。即蔡与流之外。不在五服之内者。亦是夷蛮之地。试以下文观之。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若谓非蛮非夷。只是空荒无人之地。则夫安有声教之可讫也哉。
矣。况历夏殷千有馀年。其制安得无改也。然五服九服。其名虽异。而其地不甚加广。先儒谓禹则方直而计之。后世以人迹屈曲而量之。或谓古今尺度长短不齐。未知何说为是。要之周时职方。宲未尝三倍于尧也。孔传五服之名。虽各有义。其说大抵迂回。蔡传不取之是也。蔡与流。虽在夷蛮之外。其地则仍是夷与蛮也。特以罪人所居。故另有蔡与流之名。非惟此地为然。即蔡与流之外。不在五服之内者。亦是夷蛮之地。试以下文观之。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若谓非蛮非夷。只是空荒无人之地。则夫安有声教之可讫也哉。上问曰。甸服独言赋。而四服不言何也。虽云推甸服以见其四。然粟米之赋。则似不及于荒服。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甸服天子所治。故赋法独详。而井地什一之制。达于天下。亦当视此为例。若夫要荒二服。未必尽同内地。只应存其大体而已。
上问曰。秪台德先。不距朕行。史臣记之。而曰台曰朕何也。岂载禹之言如此欤。
臣书九对曰。曰台曰朕。虽似自称。然全篇揔是纪事。则不应此二句独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6L 页
 为禹所言。是乃史臣赞禹之词。盖述禹意若曰。以敬吾之德为先。则天下不能违越吾之所行也云尔。
为禹所言。是乃史臣赞禹之词。盖述禹意若曰。以敬吾之德为先。则天下不能违越吾之所行也云尔。上问曰。玄圭舜命禹治水时。以此圭赐之而禹受之。功成后还纳于舜。如后世纳符之类欤。
臣书九对曰。史记及孔传。并云尧赐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蔡传则谓禹以玄圭为贽而告成功于舜。两说俱似未备。鲧是崇伯。禹既嗣为诸侯。则自当班瑞于治水之初。及其成功。又当执此为贽。以告于上。然则谓尧赐禹。还恐得之。
李秉模问曰。冀是帝都。治水在所当先。而河不下泄。水无去处。则虽是帝都。其可得强以先之耶。
书九曰。孔疏云冀兖二州之水。各自东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经兖州。故先从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东入兖州。水无去处。治之无益。虽是帝都。不得先也。其言是矣。
甘誓
上问曰。大战于甘之上。当有王与有扈四字而无之何欤。
臣书九对曰。王者有征无战。而书曰大战于甘。已著有扈不臣之罪。若更加王与有扈四字。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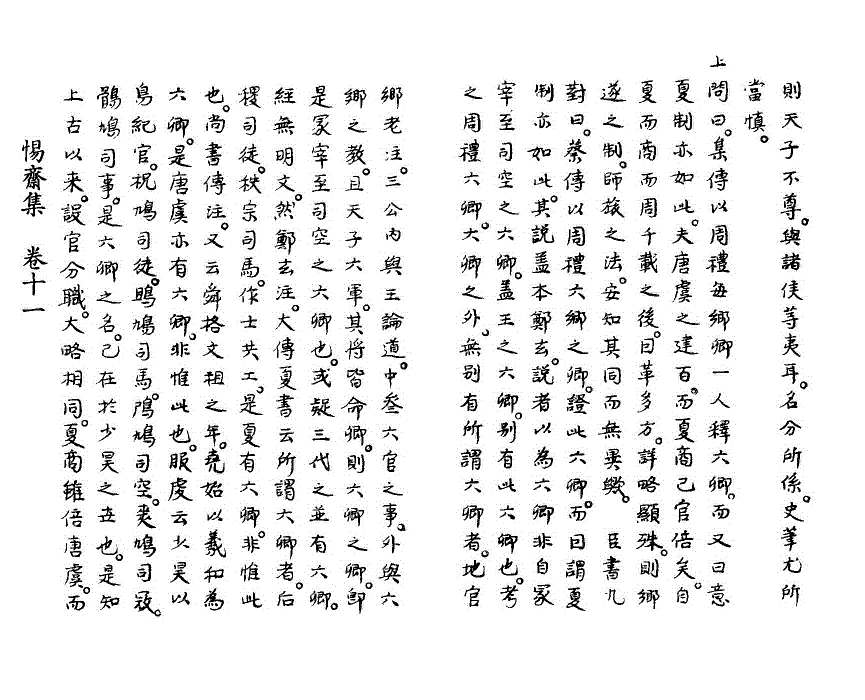 则天子不尊。与诸侯等夷耳。名分所系。史笔尤所当慎。
则天子不尊。与诸侯等夷耳。名分所系。史笔尤所当慎。上问曰。集传以周礼每乡卿一人释六卿。而又曰意夏制亦如此。夫唐虞之建百。而夏商已官倍矣。自夏而商而周千载之后。因革多方。详略显殊。则乡遂之制。师旅之法。安知其同而无异欤。
臣书九对曰。蔡传以周礼六乡之卿。證此六卿。而因谓夏制亦如此。其说盖本郑玄。说者以为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盖王之六卿。别有此六卿也。考之周礼六卿。六卿之外。无别有所谓六卿者。地官乡老注。三公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乡之教。且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则六卿之卿。即是冢宰至司空之六卿也。或疑三代之并有六卿。经无明文。然郑玄注。大传夏书云所谓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是夏有六卿。非惟此也。尚书传注。又云舜格文祖之年。尧始以羲和为六卿。是唐虞亦有六卿。非惟此也。服虔云少昊以鸟纪官。祝鸠司徒。鴡鸠司马。鸤鸠司空。爽鸠司寇。鹘鸠司事。是六卿之名。已在于少昊之世也。是知上古以来。设官分职。大略相同。夏商虽倍唐虞。而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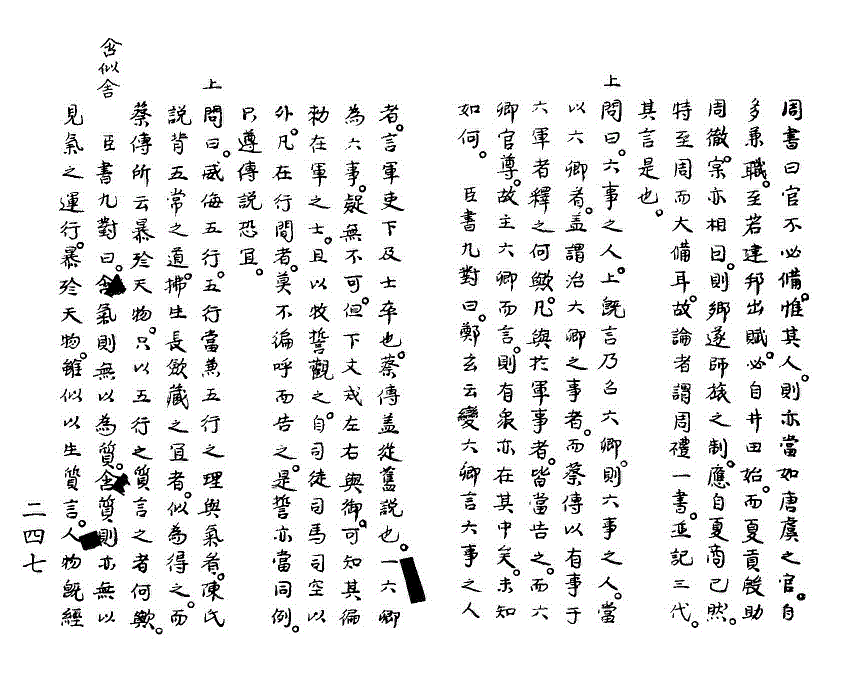 周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则亦当如唐虞之官。自多兼职。至若建邦出赋。必自井田始。而夏贡殷助周彻。宲亦相因。则乡遂师旅之制。应自夏商已然。特至周而大备耳。故论者谓周礼一书。并记三代。其言是也。
周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则亦当如唐虞之官。自多兼职。至若建邦出赋。必自井田始。而夏贡殷助周彻。宲亦相因。则乡遂师旅之制。应自夏商已然。特至周而大备耳。故论者谓周礼一书。并记三代。其言是也。上问曰。六事之人。上既言乃召六卿。则六事之人。当以六卿看。盖谓治六卿之事者。而蔡传以有事于六军者释之何欤。凡与于军事者。皆当告之。而六卿官尊。故主六卿而言。则有众亦在其中矣。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郑玄云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蔡传盖从旧说也。一六卿为六事。疑无不可。但下文戒左右与御。可知其遍敕在军之士。且以牧誓观之。自司徒司马司空以外。凡在行间者。莫不遍呼而告之。是誓亦当同例。只遵传说恐宜。
上问曰。威侮五行。五行当兼五行之理与气看。陈氏说背五常之道。拂生长敛藏之宜者。似为得之。而蔡传所云暴殄天物。只以五行之质言之者何欤。
臣书九对曰。含(含似舍)气则无以为质。含(含似舍)质则亦无以见气之运行。暴殄天物。虽似以生质言。人物既经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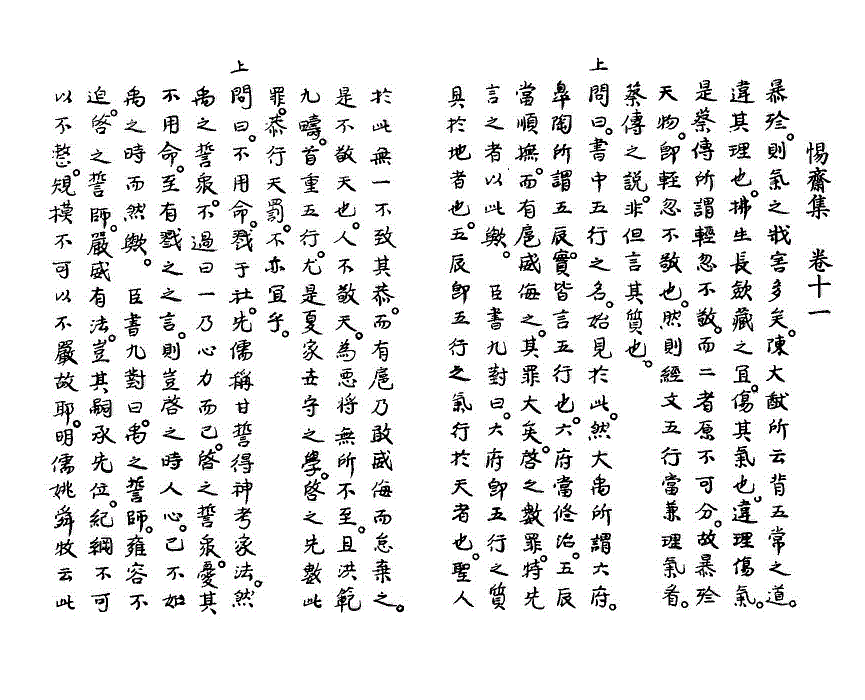 暴殄。则气之戕害多矣。陈大猷所云背五常之道。违其理也。拂生长敛藏之宜。伤其气也。违理伤气。是蔡传所谓轻忽不敬。而二者原不可分。故暴殄天物。即轻忽不敬也。然则经文五行当兼理气看。蔡传之说。非但言其质也。
暴殄。则气之戕害多矣。陈大猷所云背五常之道。违其理也。拂生长敛藏之宜。伤其气也。违理伤气。是蔡传所谓轻忽不敬。而二者原不可分。故暴殄天物。即轻忽不敬也。然则经文五行当兼理气看。蔡传之说。非但言其质也。上问曰。书中五行之名。始见于此。然大禹所谓六府。皋陶所谓五辰。实皆言五行也。六府当修治。五辰当顺抚。而有扈威侮之。其罪大矣。启之数罪。特先言之者以此欤。
臣书九对曰。六府即五行之质具于地者也。五辰即五行之气行于天者也。圣人于此无一不致其恭。而有扈乃敢威侮而怠弃之。是不敬天也。人不敬天。为恶将无所不至。且洪范九畴。首重五行。尤是夏家世守之学。启之先数此罪。恭行天罚。不亦宜乎。
上问曰。不用命。戮于社。先儒称甘誓得神考家法。然禹之誓众。不过曰一乃心力而已。启之誓众。忧其不用命。至有戮之之言。则岂启之时人心。已不如禹之时而然欤。
臣书九对曰。禹之誓师。雍容不迫。启之誓师。严威有法。岂其嗣承先位。纪纲不可以不整。规模不可以不严故耶。明儒姚舜牧云此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8L 页
 可徵世道之一变信矣。
可徵世道之一变信矣。五子之歌
上问曰。自太康至作歌。是史氏叙五子作歌之由也。其曰黎民咸贰。其曰因民不忍。再提出民字。以见与皇祖民可近之训相反。又以为予临兆民。凛若朽索御六马之语张本。可谓深得五子之情矣。如是看。果得史氏本意否。或曰。非史氏叙之也。乃五子自叙也。未知然否。
臣书九对曰。五子之歌。忧闵宗国至诚恻怛之意。溢于辞表。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为一篇宗旨。故史氏叙之如此。以明其致乱之由。专在民心之离贰。垂戒深切矣。若以此为五子自叙。则道理恐不当若此。仇予之予。指太康而犹不忍斥言。况直书君父之失德。自述其作诗之义。以诏天下后世。则其如为亲者讳何哉。
上问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此歌是五子自言其悲怨之志而已耶。抑陈奏于太康。如谏书之为耶。诗言志歌永言。歌亦诗也。可见其性情。而歌有敦厚温柔之意。则五子其贤矣欤。
臣书九对曰。五子见宗社之将亡。而忠不自达。力无所施。故作此歌。以叙其忧郁怨怅(怅似恨)之情也。是时太康在洛。后羿距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9H 页
 河。虽欲纳谏。恐不可及矣。然天下闻之。莫不怛然动心。咸思兴复。羿浞之诛。未必不由于此歌之力。岂不贤哉。
河。虽欲纳谏。恐不可及矣。然天下闻之。莫不怛然动心。咸思兴复。羿浞之诛。未必不由于此歌之力。岂不贤哉。上问曰。一人三失。蔡传曰所失者众也。是言过失甚多。非一二也。陈氏引频复之凶之文。是言乍改而复为至于三也。两说不同。当从蔡传欤。
臣书九对曰。下文云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三失乎。然则蔡传固是正训。而陈说亦切于事情。一失至于三而不变。不可望其复改矣。此五子之所以怨也。观此可知其周旋左右。朝夕规谏。非止一再。若使平日默无一言。至此而遽恐(恐似怨)。亦非仁人之心。两说不妨并存矣。
上问曰。太康但有禽荒之失。而声色沉湎高(高字下似有大字)宫室之事。则皆无之欤。既以逸豫灭德。又云一人三失。则禽荒之外。岂无他过恶乎。然以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文观之。一犹必亡。辞意愈严。太康之但有禽荒典五愆具备。固不必论也欤。
臣书九对曰。本心一亡。众邪皆集。太康既以逸豫灭德。是乃亡其本心也。虽因禽荒而丧国。可知其平日过失。非止此一事。五子之历数五愆。终之以一犹必亡者。盖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49L 页
 伤其失德既多。亡徵已久也。
伤其失德既多。亡徵已久也。上问曰。惟彼陶唐。既述皇祖之戒。而必引陶唐何也。欲溯其源而言之。以见圣祖之与尧一揆欤。
臣书九对曰。皇祖遗基。固当敬守。况此冀方。传自陶唐。则皇祖亦有所受之矣。后王尤安敢忽乎。太康不念于此。轻弃国都。畋于洛表。使冀方之地。一朝入于羿。益可痛心。故溯其本而言之也。
上问曰。关石和匀之传曰。法度之制始于权云云。而考之舜与之传。则律起于黄钟。而度生于黄钟之长。量生于黄钟之容。衡生于黄钟之容之重。则乃法度之制始于律也。是将安所从也。
臣书九对曰。律起黄钟。度量衡由是而生焉。此云法度之制始于权。疑若与汉志有异。盖权与物匀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则权衡宲为法度之所自出。然权之为物。本无定分。随物之轻重。而大小亦随而变。苟不一定其制。同其不齐。则诈伪百出而天下之纲纪紊矣。如欲参酌得中。黄钟之律是已。故必以一千二百黍之重为之本。而铢两斤石。自此益加。然则权为法度之始。律又权之始也。汉志蔡传。互相发明。初无异同。恐不可执此而疑彼也。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0H 页
 上问曰。虽悔可追。凡人臣之戒其君。当有王庶几改之。犹可及止之之意。而今曰虽悔可追。似若以为悔之无及。而绝望于其君何也。岂以太康之失德。终不可移而然欤。抑以强臣距河。天下之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而然欤。
上问曰。虽悔可追。凡人臣之戒其君。当有王庶几改之。犹可及止之之意。而今曰虽悔可追。似若以为悔之无及。而绝望于其君何也。岂以太康之失德。终不可移而然欤。抑以强臣距河。天下之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而然欤。臣书九对曰。虽悔可追云者。若在太康未失国之前而进此语。则是乃戒之之切也。若在太康已失国之后而有此语。则是乃怨之之深也。由前由后。俱无可嫌。况今失德已彰。乱形已成。又安得无绝望之意乎。绝望者即所以望之也。可谓忠厚之至矣。
胤征
上问曰。承王命三字甚有力。可见仲康之尚能号令也。羿则未及讨而先诛羲和。固其时形势为然。而春秋之法。先治其党与。则先诛羲和。于义亦所当然欤。
臣书九对曰。仲康肇位。自二孔以为羿废太康所立。苏轼至以为羲和贰于羿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蔡传不取其说而从林之奇说。然于仲康德羿。紾兄之嫌。未有以释之也。据朱子所称袁道洁说。则是时羿据河北。仲康在河南。断非羿所拥立。故金履祥通鉴前编。力辨旧说。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0L 页
 仲康虽立国于外。此云肇位四海。春秋大一统之义。固已森然。又云。承王命徂征。则征伐自天子出矣。特因势弱。不能遽讨羿。而先征羲和。剪其羽翼。其规模举措。已自过人。假之以年。岂不能讨灭强臣。光复旧业乎。
仲康虽立国于外。此云肇位四海。春秋大一统之义。固已森然。又云。承王命徂征。则征伐自天子出矣。特因势弱。不能遽讨羿。而先征羲和。剪其羽翼。其规模举措。已自过人。假之以年。岂不能讨灭强臣。光复旧业乎。上问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常刑于五刑。为何刑耶。汤之官刑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夏之时。亦用墨刑欤。
臣书九对曰。不恭之罪。虽未知当服何刑。而不匡者墨。著在官刑。想必有自来矣。郑玄周礼注。夏刑劓墨各千。孔氏于吕刑序。亦云训夏赎刑。则夏用墨刑。从可知也。
上问曰。有扈威侮五行而讨之。则羲和之俶扰天纪。虽非党羿之事。当诛无疑欤。
臣书九对曰。羲和为历象之官。乃反俶扰天纪。其罪固大。而至于篇末。直有胁从旧染之语。则嗣位之初。即命徂征。政由党羿之罪。但不能讨羿而先讨羲和。故姑不明言其罪。只以俶扰天纪为之辞旨。
上问曰。先时不及时。是言历法推步之错误。而四时节气有先后之差也。与日食不干。且篇内所言。非以致日食为羲和之罪。以日食而罔闻知为罪。则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1H 页
 引政典之文者。盖言与先时不及时者同其罪云欤。
引政典之文者。盖言与先时不及时者同其罪云欤。臣书九对曰。日月当食之时刻分秒。一或不合。亦由历法推步之疏。先时不及时。不可但以四时节气弦望晦朔之差言之也。日食固非羲和之罪。然食限差误。历官尚难免常刑。况沈酗昏迷。全无闻知者乎。第以推步小误。概施杀无赦之刑。似太重。是可疑也。林之奇欲自政典以下。属之下文以为誓师之辞。果未知其信然否也。
上问曰。虑玉石之俱焚。胁从罔治。旧染咸新。则蔼然有好生之意。此非胤侯之自言。宲以仲康之言而宣之欤。然则仲康之不失君位。其以是欤。
臣书九对曰。胤侯承命徂征。则生杀刑赦。必当上禀天子。不敢自专。而兵者不得已用之。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宲为万世讨罪之权衡。大哉王言。非仲康之仁胤侯之贤。安能若是。
上问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此当于戎事言之。他事则不必然欤。威克爱克。似有偏底意。且爱者姑息之谓。而甘誓末段蔡传论罚不及嗣处。以爱克厥威言之。圣人亦有爱克欤。
臣书九对曰。爱有姑息之爱。有当理之爱。当理之爱。宜克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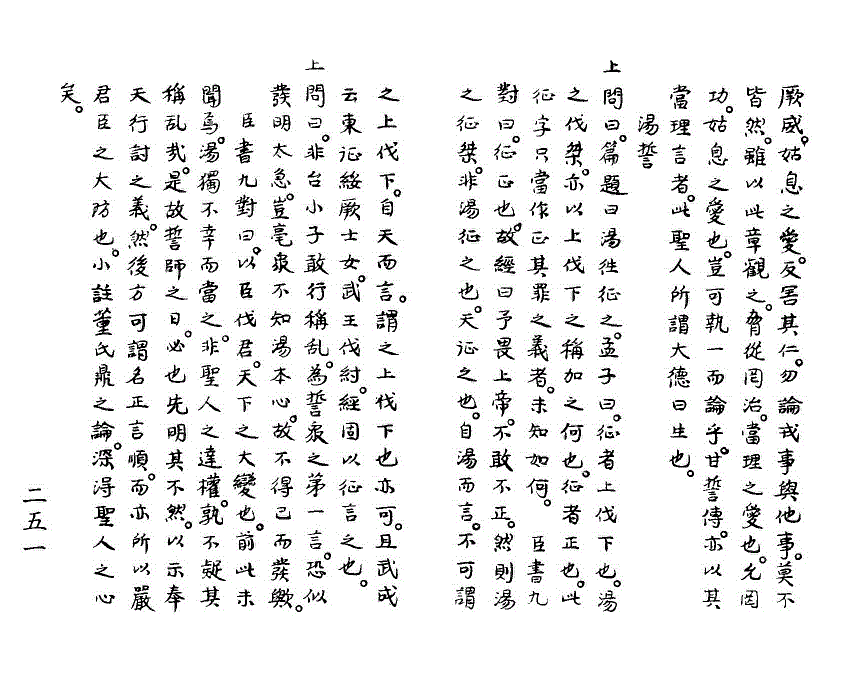 厥威。姑息之爱。反害其仁。勿论戎事与他事。莫不皆然。虽以此章观之。胁从罔治。当理之爱也。允罔功。姑息之爱也。岂可执一而论乎。甘誓传。亦以其当理言者。此圣人所谓大德曰生也。
厥威。姑息之爱。反害其仁。勿论戎事与他事。莫不皆然。虽以此章观之。胁从罔治。当理之爱也。允罔功。姑息之爱也。岂可执一而论乎。甘誓传。亦以其当理言者。此圣人所谓大德曰生也。汤誓
上问曰。篇题曰汤往征之。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汤之伐桀。亦以上伐下之称加之何也。征者正也。此征字只当作正其罪之义者。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征正也。故经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然则汤之征桀。非汤征之也。天征之也。自汤而言。不可谓之上伐下。自天而言。谓之上伐下也亦可。且武成云东征绥厥士女。武王伐纣。经固以征言之也。
上问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为誓众之第一言。恐似发明太急。岂亳众不知汤本心。故不得已而发欤。
臣书九对曰。以臣伐君。天下之大变也。前此未闻焉。汤独不幸而当之。非圣人之达权。孰不疑其称乱哉。是故誓师之日。必也先明其不然。以示奉天行讨之义。然后方可谓名正言顺。而亦所以严君臣之大防也。小注董氏鼎之论。深得圣人之心矣。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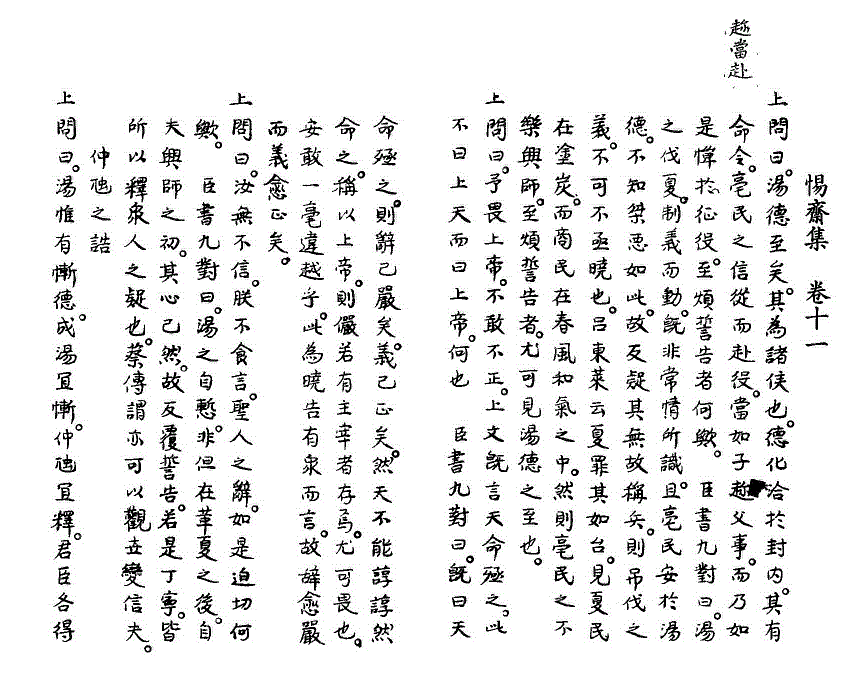 上问曰。汤德至矣。其为诸侯也。德化洽于封内。其有命令。亳民之信从而赴役。当如子赴父事。而乃如是惮于征役。至烦誓告者何欤。
上问曰。汤德至矣。其为诸侯也。德化洽于封内。其有命令。亳民之信从而赴役。当如子赴父事。而乃如是惮于征役。至烦誓告者何欤。臣书九对曰。汤之伐夏。制义而动。既非常情所识。且亳民安于汤德。不知桀恶如此。故反疑其无故称兵。则吊伐之义。不可不亟晓也。吕东莱云夏罪其如台。见夏民在涂炭。而商民在春风和气之中。然则亳民之不乐兴师。至烦誓告者。尤可见汤德之至也。
上问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上文既言天命殛之。此不曰上天而曰上帝。何也。
臣书九对曰。既曰天命殛之。则辞已严矣。义已正矣。然天不能谆谆然命之。称以上帝。则俨若有主宰者存焉。尤可畏也。安敢一毫违越乎。此为晓告有众而言。故辞愈严而义愈正矣。
上问曰。汝无不信。朕不食言。圣人之辞。如是迫切何欤。
臣书九对曰。汤之自惭。非但在革夏之后。自夫兴师之初。其心已然。故反覆誓告。若是丁宁。皆所以释众人之疑也。蔡传谓亦可以观世变信夫。
仲虺之诰
上问曰。汤惟有惭德。成汤宜惭。仲虺宜释。君臣各得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2L 页
 其道欤。
其道欤。臣书九对曰。汤若不惭。非圣人重伦纲之心。仲虺若不释惭。无以明圣人不得已之心。上下俱得其道。吕东莱说已言之。
上问曰。成汤之有惭德。盖以为古无此事。而五帝本纪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云云。则征伐而有天下。已有行之矣。来世口实。成汤何为取而自当也。
臣书九对曰。黄帝始用干戈。故史记云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说宲本贾谊新书。谊之言又出于国语。盖唐虞以上之事。不见诗书。后世所传。类多汉儒傅会。本不足深信。故古昔人君征伐而有天下者。其显著可徵。无如成汤。汤之恐来世以己为口实。固其宜也。且君臣之分。天下之大防。干戈圣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汤之伐桀。虽应天顺人。然承舜禹授受之后。其心终不能自安。使黄帝诚有是事。以圣人忧天下虑万世之心。亦岂可援以自解。视以为当然之道也哉。成汤之自讼惭德。政所以为成汤也。前此帝王之行与不行。恐不须问也。
上问曰。用爽厥师。或言非谓昭明其众庶。是谓用明其军师。盖上言夏王有罪。此当指言征伐之事。此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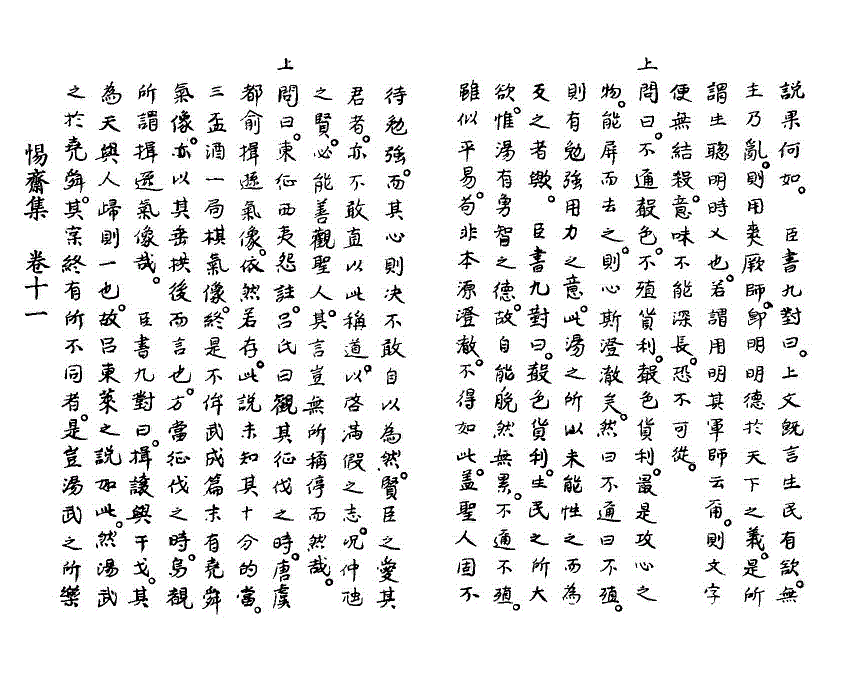 说果何如。
说果何如。臣书九对曰。上文既言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则用爽厥师。即明明德于天下之义。是所谓生聪明时乂也。若谓用明其军师云尔。则文字便无结杀。意味不能深长。恐不可从。
上问曰。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声色货利。最是攻心之物。能屏而去之。则心斯澄澈矣。然曰不迩曰不殖。则有勉强用力之意。此汤之所以未能性之而为反之者欤。
臣书九对曰。声色货利。生民之所大欲。惟汤有勇智之德。故自能脱然无累。不迩不殖。虽似平易。苟非本源澄澈。不得如此。盖圣人固不待勉强。而其心则决不敢自以为然。贤臣之爱其君者。亦不敢直以此称道。以启满假之志。况仲虺之贤。必能善观圣人。其言岂无所称停而然哉。
上问曰。东征西夷怨注。吕氏曰观其征伐之时。唐虞都俞揖逊气像。依然若存。此说未知其十分的当。三杯酒一局棋气像。终是不侔武成篇末有尧舜气像。亦以其垂拱后而言也。方当征伐之时。乌睹所谓揖逊气像哉。
臣书九对曰。揖让与干戈。其为天与人归则一也。故吕东莱之说如此。然汤武之于尧舜。其宲终有所不同者。是岂汤武之所乐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3L 页
 为哉。所遇之时不幸而然。惟其征伐之际。雍容不迫。尚能如是。此所以为圣人也欤。
为哉。所遇之时不幸而然。惟其征伐之际。雍容不迫。尚能如是。此所以为圣人也欤。上问曰。朱子曰推亡。只是说伐桀。而蔡传以弱昧乱亡为诸侯之事何也。
臣书九对曰。朱子此言。盖从疏说。然前既释汤之惭。此是劝勉之事。若以弱昧乱亡。属之于桀。则汤固已伐桀矣。更无待乎仲虺之劝勉。故蔡传以诸侯言之也。
上问曰。建中于民。是先立于己。而推而立于民之谓欤。以大学之道言之。懋昭大德是明德。建中是新民。中是至善之所在欤。建中之义。与建极同欤异欤。
臣书九对曰。上帝降衷。故民莫不有是中。是所谓至善之所在也。王者光明其德。立中道于天下。己之中。乃民所由中也。故曰建中于民。然建中与建极。亦有同异。只以人君正身。作民准则之义言之。则建中即建极也。若训极为中。则朱子断言其非。恐不可混并为说。
上问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先言义后言礼。先言事后言心。此与直内方外之序不同。何欤。
臣书九对曰。敬与义对。则敬主乎内。义形乎外。义与礼对。则事在外而义由内。制心在内而礼由外作。故彼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4H 页
 此所言先后不同矣。
此所言先后不同矣。上问曰。能自得师者王。此自字与自满自用之自。宜无二义。而小注陈氏说。以此自字为自然之自。谓尊德乐道。出于中心之自然。恐非是。盖言自己之能得师。如曰吾师我师。岂非以自己上亲切而云欤。
臣书九对曰。尊德乐道。出于中心之自然。故不因乎人。而自己能得师。陈氏经说似无可疑。且引自明自强为證。则是陈氏亦以此自字为自己之自也。恐当与自满自用之自一例看。
吴载纯问曰。德懋懋官。传曰懋茂也。又曰与懋哉之义同。其义似不同。然则此四懋字当作何解欤。
书九曰。懋有二义。一是繁多之意。一是劝勉之意。其义亦必相因而成。试以此章论之。人能劝勉于功德。然后功德方能繁多。上之人所以繁多其官赏者。政是以官赏劝勉之也。蔡传必兼二义而言者是也。
李秉模问曰。兼弱推亡。固是天道之自然也。圣人何尝容心于其间哉。然其兼之也推之也。盖出于不得已。而恻怛之意。未始不行于誓诰之际。则虺于释惭之诰。何无一言宛转。直谓以邦乃其昌耶。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4L 页
 书九曰。圣人之兼弱推亡。固无一毫私意。况汤之伐夏。尤是应天顺人。然其所以忧愧悯伤者溢于辞表。恻怛之心。固已行于其间矣。仲虺方将释汤之惭。则不必更作婉辞。正宜直截为言。故首以表正万邦奉若天讨。以明天理之不得不然。又推及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义。而直以邦乃其昌继之。此盖本于释惭之意也。虽然昌邦之道。岂惟在于推亡固存而已哉。下文所谓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以至于慎终惟始。其反覆戒告。未尝不丁宁恳切。要在该贯而领会之而已。
书九曰。圣人之兼弱推亡。固无一毫私意。况汤之伐夏。尤是应天顺人。然其所以忧愧悯伤者溢于辞表。恻怛之心。固已行于其间矣。仲虺方将释汤之惭。则不必更作婉辞。正宜直截为言。故首以表正万邦奉若天讨。以明天理之不得不然。又推及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义。而直以邦乃其昌继之。此盖本于释惭之意也。虽然昌邦之道。岂惟在于推亡固存而已哉。下文所谓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以至于慎终惟始。其反覆戒告。未尝不丁宁恳切。要在该贯而领会之而已。汤诰
上问曰。降衷之衷。朱子以中字言之。此是未发之中欤。恒性之性。是天命之性欤。未发之中。自子思始言之。则汤之意未必及乎此也。天命之性。兼人物言。而恒性独为民言。则恐不可谓天命之性。然则降衷之衷。只当作尧舜执中之中看。恒性之性。只当作孟子性善之性看欤。若之为言顺也。人顺之耶。如曰人顺之。则恐涉容力。只是自然之谓欤。
臣书九对曰。未发之中。执中之中。元非二物。理具于内而不偏不倚者。是谓未发之中。中之体也。情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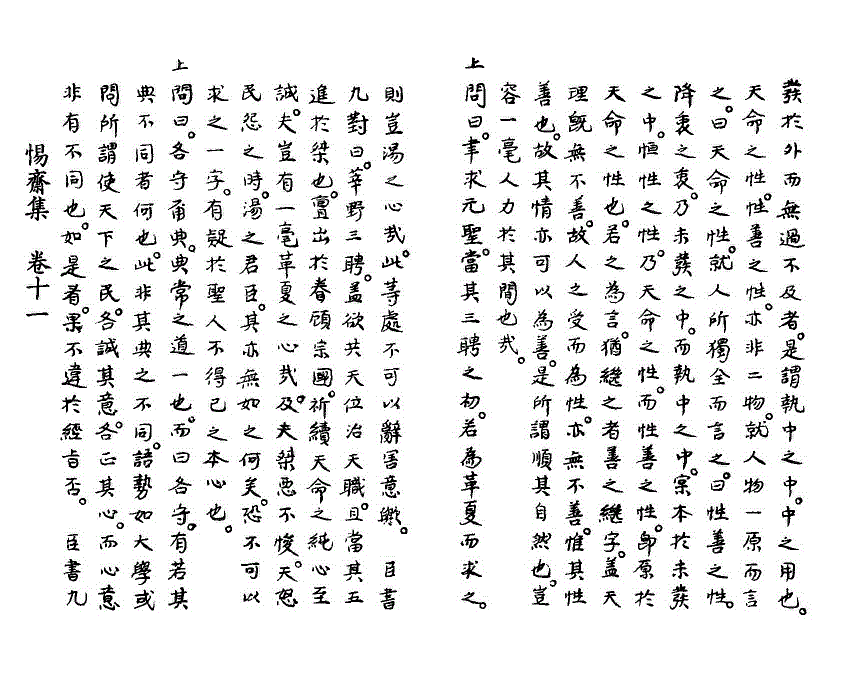 发于外而无过不及者。是谓执中之中。中之用也。天命之性。性善之性。亦非二物。就人物一原而言之。曰天命之性。就人所独全而言之。曰性善之性。降衷之衷。乃未发之中。而执中之中。宲本于未发之中。恒性之性。乃天命之性。而性善之性。即原于天命之性也。若之为言。犹继之者善之继字。盖天理既无不善。故人之受而为性。亦无不善。惟其性善也。故其情亦可以为善。是所谓顺其自然也。岂容一毫人力于其间也哉。
发于外而无过不及者。是谓执中之中。中之用也。天命之性。性善之性。亦非二物。就人物一原而言之。曰天命之性。就人所独全而言之。曰性善之性。降衷之衷。乃未发之中。而执中之中。宲本于未发之中。恒性之性。乃天命之性。而性善之性。即原于天命之性也。若之为言。犹继之者善之继字。盖天理既无不善。故人之受而为性。亦无不善。惟其性善也。故其情亦可以为善。是所谓顺其自然也。岂容一毫人力于其间也哉。上问曰。聿求元圣。当其三聘之初。若为革夏而求之。则岂汤之心哉。此等处不可以辞害意欤。
臣书九对曰。莘野三聘。盖欲共天位治天职。且当其五进于桀也。亶出于眷顾宗国。祈续天命之纯心至诚。夫岂有一毫革夏之心哉。及夫桀恶不悛。天怒民怨之时。汤之君臣。其亦无如之何矣。恐不可以求之一字。有疑于圣人不得已之本心也。
上问曰。各守尔典。典常之道一也。而曰各守。有若其典不同者何也。此非其典之不同。语势如大学或问所谓使天下之民。各诚其意。各正其心。而心意非有不同也。如是看。果不违于经旨否。
臣书九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5L 页
 对曰。礼乐政教。自有一王之制。是所谓典也。凡在侯邦。皆当恪守。则此各字。与或问之各字义亦不殊。若就所共守之中。分而言之。伦彝纲常。天下所同。至于仪文制度。上下尊卑等威斯别。其所当守之典。又各随分不同。与正心诚意之人无不同者。恐或差间。
对曰。礼乐政教。自有一王之制。是所谓典也。凡在侯邦。皆当恪守。则此各字。与或问之各字义亦不殊。若就所共守之中。分而言之。伦彝纲常。天下所同。至于仪文制度。上下尊卑等威斯别。其所当守之典。又各随分不同。与正心诚意之人无不同者。恐或差间。上问曰。罪在朕躬。不敢自赦。蔡传以自恕释自赦。恕字本以如心而得名。可以施于人。不可施于己。朱子于大学或问。论之详矣。蔡氏岂不闻朱子之论。而乃袭范氏之谬欤。自恕改以自容。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恕字注疏家多作宽假之称。毋论人己。一例宽假。则治己不严。爱己太薄而其责之于人者。又不免姑息之归矣。故程子直以如心为训。而朱子又详辨于大学或问。蔡传云云。只是泛说。故偶借宽假之意。以释赦字。非欲有违于朱子之论而然也。若必以恕不可施于己为嫌。则改安他字。亦恐无妨。
上问曰。叹息言尚克时忱。乃亦有终。戒饬之意深矣。上文虽有朕躬不敢赦。万方在一人等语。不过论君道之当然。慰民望于新服而已。此篇本为诏诰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6H 页
 万方而作。无缘却有箴儆君德之意。吴氏所谓兼人己而言者何也。
万方而作。无缘却有箴儆君德之意。吴氏所谓兼人己而言者何也。臣书九对曰。圣人慎始图终。虽在安常无事之日。其心未尝不慥慥也。况乎伐罪吊民。革命建国。其时之艰。其事之重。果何如也。方将立一代之规模。新兆民之耳目。以垂亿万年之基业。安得无上下交儆。思与天下更始哉。故此篇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盖极本溯源。发前圣之所未发。中又以奉天行讨守邦承休之意。反覆诏诰。而又皆薄责于人。厚责于己。末乃继之以尚克时忱乃亦有终。其丁宁恻怛之意。足可以孚信于万邦。夫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天下万事。不本于其身。而欲人之从我者。未之有也。然则此篇虽是告下之辞。吴棫所谓兼人己而言者。岂不信然矣乎。呜呼。此所以为圣人之言也夫。
伊训
上问曰。惟元祀。蔡传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按礼。崩年即位。踰年改元。而此云即位之元年何也。与其下文引苏氏说以为崩年改元乱世事。以驳孔氏之谬者相矛盾。抑又何也。
臣书九对曰。古者即位之年有三焉。三年丧毕而即位者舜也。练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6L 页
 而祔。祔而即位者殷礼也。踰年正月而即位者周礼也。崩年即位。又是周家之变礼也。仲壬盖以前年十二月崩。至此而练。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者。既练而祔于庙也。先君祔庙之后。嗣子即位。则是年为即位之元年。故下篇惟三祀十有二月。蔡传云太甲终丧明年之正朔也。二年为终丧之年。则即位元年。可知其非崩年也。世变愈下。而崩年即位。始为后代之通礼。殷时则必无此事。而蔡传又取吴氏说。谓太甲即位于仲壬之柩前。恐未免自乱其例矣。
而祔。祔而即位者殷礼也。踰年正月而即位者周礼也。崩年即位。又是周家之变礼也。仲壬盖以前年十二月崩。至此而练。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者。既练而祔于庙也。先君祔庙之后。嗣子即位。则是年为即位之元年。故下篇惟三祀十有二月。蔡传云太甲终丧明年之正朔也。二年为终丧之年。则即位元年。可知其非崩年也。世变愈下。而崩年即位。始为后代之通礼。殷时则必无此事。而蔡传又取吴氏说。谓太甲即位于仲壬之柩前。恐未免自乱其例矣。上问曰。祠于先王。吴氏曰遍祠于先王。陈氏亦谓如玄王之类。而蔡传则以先王为汤何也。
臣书九对曰。先王与厥祖。皆是指汤而言。但摄祭者伊尹也。祗见者嗣王也。自伊尹而言之曰先王。自嗣王而言之曰厥祖。故蔡传之训如此。然既告汤庙。则馀庙自当遍告。吴氏陈氏之说。亦非无据。而此篇所训。皆是烈祖之成德。终当以汤为主也。
上问曰。方懋厥德。方字只是方当其时之谓。而陈氏欲作方将之义看。以为方见其进。未见其止之意。恐伤巧。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以方字为方将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7H 页
 之方。于劝勉嗣王之义。似尤紧切。故陈大猷说如此。但方将者未然之辞。鬼神皆宁。鱼鳖咸若。乃是功化之极致。人君将欲懋德。而其效安能便至于此。然则只作方当之方。语意圆全。方将之意。亦已包在其中矣。
之方。于劝勉嗣王之义。似尤紧切。故陈大猷说如此。但方将者未然之辞。鬼神皆宁。鱼鳖咸若。乃是功化之极致。人君将欲懋德。而其效安能便至于此。然则只作方当之方。语意圆全。方将之意。亦已包在其中矣。上问曰。肇修人纪。人纪盖言三纲五常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既是言三纲。则不曰人纲而曰人纪何也。如以兼言五常而谓之纪。则朱子岂不曰仁义礼智人性之纲耶。
臣书九对曰。大曰纲。小曰纪。纪者所以维持此纲也。仁义礼智。为人性之纲。父子君臣。为人伦之纲。然其所以尽此性惇此伦者。亦有许多节目条理。是所谓纪也。若云肇修人纲。恐有遗小忽细之嫌。故曰人纪。纪修则纲自举矣。
上问曰。三风十愆。小注吕氏曰。前六愆。因后四愆而生。然则汤之言六愆于四愆之前何也。
臣书九对曰。慢圣言咈忠直。疏耆德昵顽童。是皆失其本心也。本心既失。歌舞货色游畋之事。何所不有。汤之戒。由浅而入深。自末而溯本。故叙次之先后如此。
上问曰。侮圣言。圣人之言如神明。可尊可敬。故论语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7L 页
 曰畏圣人之言。不畏而侮。则其愆大矣。侮圣言。如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之类是也。然极论之则虽口诵圣人之言。而不为服行。则亦便是侮圣言欤。
曰畏圣人之言。不畏而侮。则其愆大矣。侮圣言。如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之类是也。然极论之则虽口诵圣人之言。而不为服行。则亦便是侮圣言欤。臣书九对曰。圣人之言。罔非至理。此而可侮。馀无足畏。且其所以侮之也。有刚恶焉。有柔恶焉。言不忠信者。是刚恶也。身不服行者。是柔恶也。而朱子谓自弃之罪甚于自暴。又于论语末章集注。谆谆以侮圣言三字为戒。其义严矣。
上问曰。禹之训。汤之官刑。其揆一也。十愆之于六训。又加详焉。而峻宇雕墙。独漏于三风之目。详略之异。其义安在。
臣书九对曰。惟天生民有欲。故违理悖德之事。由是而作焉。圣人忧之。为之条教禁令约束之。然唐虞之世。罚止象刑。而降及成周。五刑之属。至于三千。岂尧舜之圣。不及穆王。皋陶之法。疏于吕侯而然哉。诚以世级愈下。事变无穷。民之过恶。或出于常情之外。虽以圣帝贤臣之智。亦不得逆料而预防之也。尧之为君。土阶三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此禹之所亲见也。峻宇雕墙之患。宜无足以费虑。桀之为君。琼室象廊。瑶其台而玉其床。其祸之烈。终至于辱身丧国而后已。此汤之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8H 页
 所亲见也。其所以监前毖后。为天下万世戒者。宜莫先于此。然而禹之训。拳拳若是。汤乃略而不言。无他。三风十愆。特举其大要而已。非独于此而忽之也。夫侮圣言逆忠直。失德之大者。纵欲败度。莫不以是为本。而禹之垂戒。又反遗其本而语其末。是岂知有所不周。虑有所不及而然哉。亦惟曰举其大要而已。夫如是。奚独于汤而疑之也。虽然既云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则是必不在于茅茨土阶之上。琼室象廊。即其末流之所当有者。由是论之。汤又未尝不言之也。呜呼。圣人之训。如彼恳恻。而汉唐以来。穷土木崇靡丽。贻讥后世者。或不能无之。又岂非明君懿辟之所宜鉴戒也哉。
所亲见也。其所以监前毖后。为天下万世戒者。宜莫先于此。然而禹之训。拳拳若是。汤乃略而不言。无他。三风十愆。特举其大要而已。非独于此而忽之也。夫侮圣言逆忠直。失德之大者。纵欲败度。莫不以是为本。而禹之垂戒。又反遗其本而语其末。是岂知有所不周。虑有所不及而然哉。亦惟曰举其大要而已。夫如是。奚独于汤而疑之也。虽然既云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则是必不在于茅茨土阶之上。琼室象廊。即其末流之所当有者。由是论之。汤又未尝不言之也。呜呼。圣人之训。如彼恳恻。而汉唐以来。穷土木崇靡丽。贻讥后世者。或不能无之。又岂非明君懿辟之所宜鉴戒也哉。上问曰。其刑墨。人主纳谏而赏谏则谏者日进。不谏之刑不必作。而必制之何也。
臣书九对曰。来谏之道。惟在于人君之虚心听纳。不谏之刑。抑亦末也。然目见君上之过失。不能匡规。要为持禄固位之计。驯致丧家亡国之祸。亦安所逃其罪乎。况导谀阿意。以启其逸欲之心者。又岂特不匡之罪而已哉。朱子曰。汤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讨。毫发不差处。此言诚可使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所警夫(夫似矣)。
惕斋集卷之十一 第 258L 页
 李秉模问曰。臣下不匡。固有罪也。而凡在绳愆纠缪之责者。皆可施以刑墨之典欤。刑之则殆不胜刑。不刑则法无以信于天下。如何为可耶。先儒所谓进而谏。未必死。退而不谏。必受刑。则虽不欲谏。亦不得不谏云者。恐未必为先王制法之本意也。
李秉模问曰。臣下不匡。固有罪也。而凡在绳愆纠缪之责者。皆可施以刑墨之典欤。刑之则殆不胜刑。不刑则法无以信于天下。如何为可耶。先儒所谓进而谏。未必死。退而不谏。必受刑。则虽不欲谏。亦不得不谏云者。恐未必为先王制法之本意也。书九曰。人主有失德。而臣下不匡。凡在绳愆纠缪之责者。厥罪惟均。然而位有尊卑。地有亲疏。亦安得人人而尽刑之。固当举其阿谀逢迎之徒。以警其(其似具)僚耳。故朱子以昌邑南唐之诸臣为證。当是之时。未尝闻龚遂,王吉,徐铉,钟谟之同被重诛也。且施墨刑者。亦必因人主之命。人主失德。至有三风十愆。则其心惟恐臣下之有谏。岂肯自犯失德。而反责臣下之不言哉。虽然人臣之道。勿问尊卑亲疏。不可以倖免常刑有所自恕。惟当极言力争。各尽其职耳。呜呼。人主有好善纳谏之宲。虽赏之而勿言。嘉谟日进。苟或不然。虽刑之而使言。谠言莫闻。藉使畏刑而强言。不过愞熟媕婀之论。是岂出于至诚爱君之义也哉。故臣下之匡与不匡。不在于刑墨之常宪。惟在于在上者之导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