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x 页
弘斋全书卷百九
经史讲义四十六○总经[四]
经史讲义四十六○总经[四]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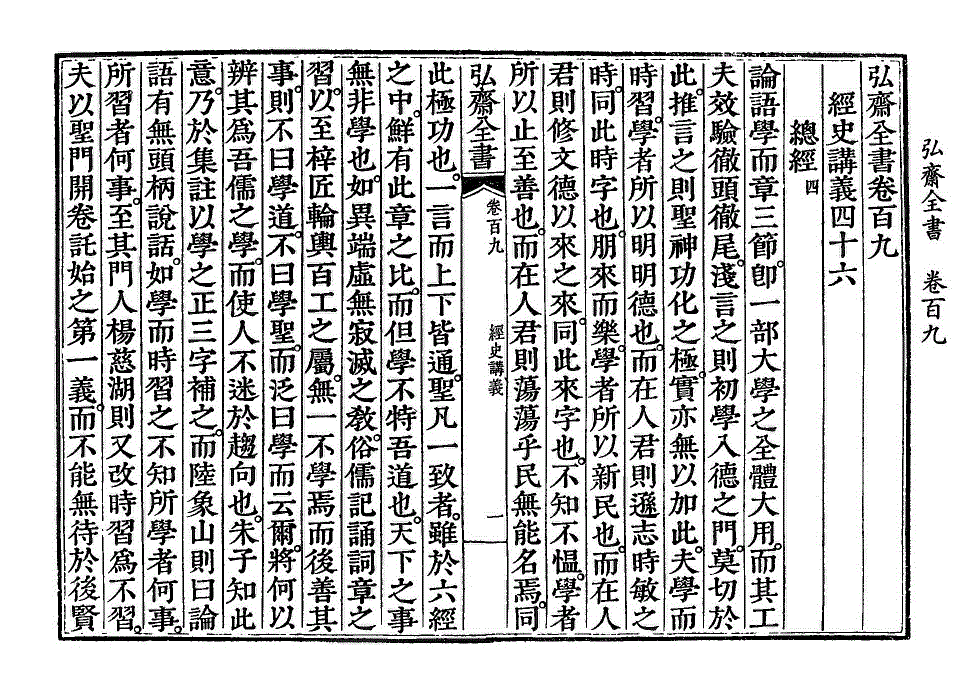 [论语]
[论语]论语学而章三节。即一部大学之全体大用。而其工夫效验彻头彻尾。浅言之则初学入德之门。莫切于此。推言之则圣神功化之极。实亦无以加此。夫学而时习。学者所以明明德也。而在人君则逊志时敏之时。同此时字也。朋来而乐。学者所以新民也。而在人君则修文德以来之来。同此来字也。不知不愠。学者所以止至善也。而在人君则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同此极功也。一言而上下皆通。圣凡一致者。虽于六经之中。鲜有此章之比。而但学不特吾道也。天下之事无非学也。如异端虚无寂灭之教。俗儒记诵词章之习。以至梓匠轮舆百工之属。无一不学焉而后善其事。则不曰学道。不曰学圣。而泛曰学而云尔。将何以辨其为吾儒之学。而使人不迷于趋向也。朱子知此意。乃于集注以学之正三字补之。而陆象山则曰论语有无头柄说话。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所学者何事。所习者何事。至其门人杨慈湖则又改时习为不习。夫以圣门开卷托始之第一义。而不能无待于后贤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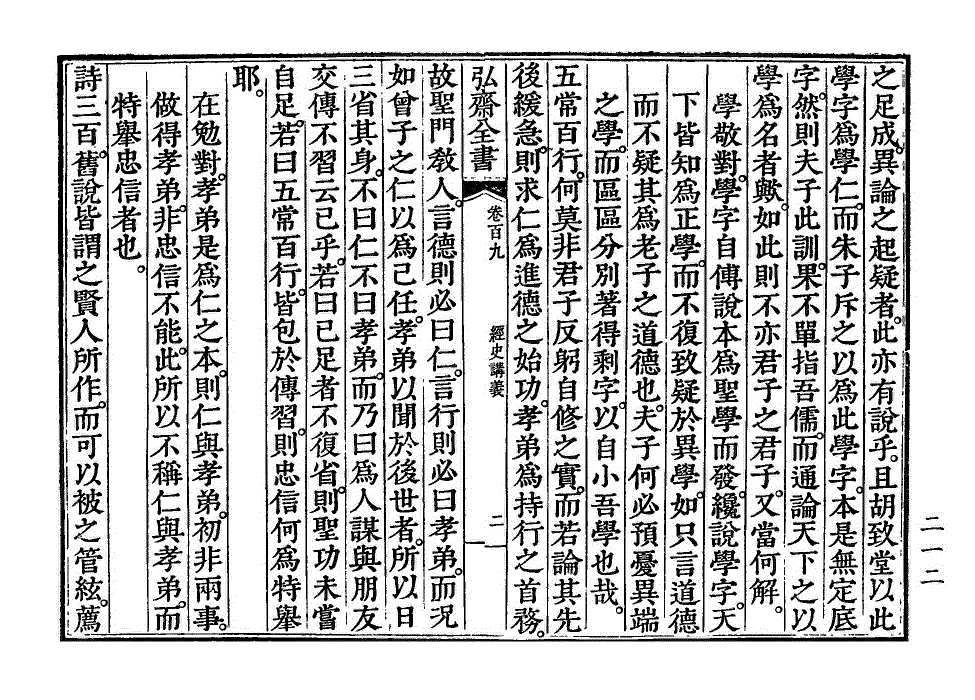 之足成。异论之起疑者。此亦有说乎。且胡致堂以此学字为学仁。而朱子斥之以为此学字。本是无定底字。然则夫子此训。果不单指吾儒。而通论天下之以学为名者欤。如此则不亦君子之君子。又当何解。
之足成。异论之起疑者。此亦有说乎。且胡致堂以此学字为学仁。而朱子斥之以为此学字。本是无定底字。然则夫子此训。果不单指吾儒。而通论天下之以学为名者欤。如此则不亦君子之君子。又当何解。学敬对。学字自傅说本为圣学而发。才说学字。天下皆知为正学。而不复致疑于异学。如只言道德而不疑其为老子之道德也。夫子何必预忧异端之学。而区区分别著得剩字。以自小吾学也哉。
五常百行。何莫非君子反躬自修之实。而若论其先后缓急。则求仁为进德之始功。孝弟为持行之首务。故圣门教人。言德则必曰仁。言行则必曰孝弟。而况如曾子之仁以为己任。孝弟以闻于后世者。所以日三省其身。不曰仁不曰孝弟。而乃曰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不习云已乎。若曰已足者不复省。则圣功未尝自足。若曰五常百行。皆包于传习。则忠信何为特举耶。
在勉对。孝弟是为仁之本。则仁与孝弟。初非两事。做得孝弟。非忠信不能。此所以不称仁与孝弟。而特举忠信者也。
诗三百。旧说皆谓之贤人所作。而可以被之管弦。荐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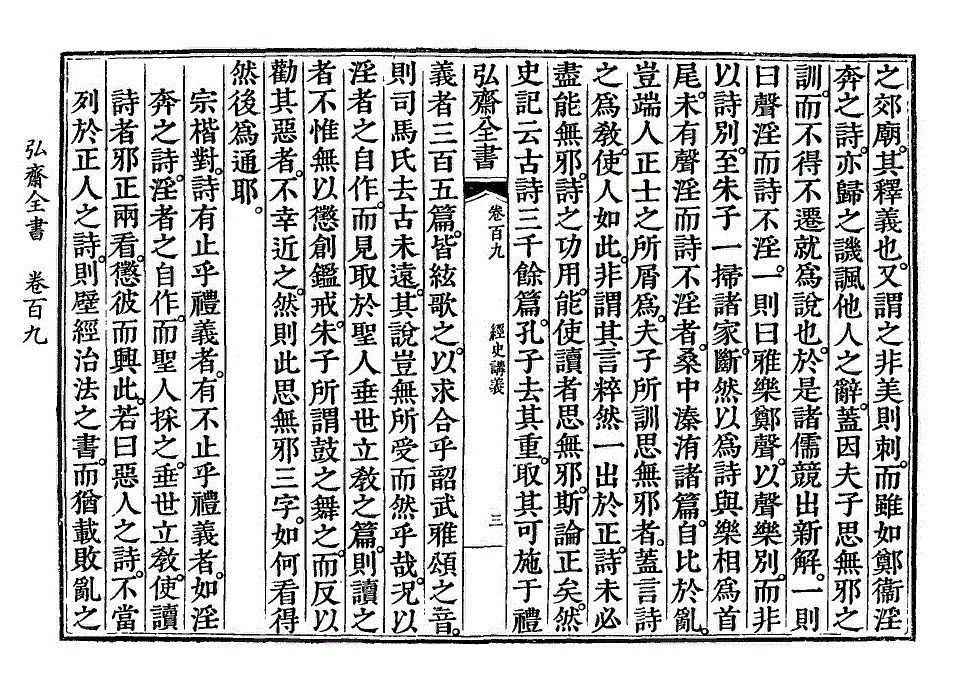 之郊庙。其释义也。又谓之非美则刺。而虽如郑卫淫奔之诗。亦归之讥讽他人之辞。盖因夫子思无邪之训。而不得不迁就为说也。于是诸儒竞出新解。一则曰声淫而诗不淫。一则曰雅乐郑声。以声乐别。而非以诗别。至朱子一扫诸家。断然以为诗与乐相为首尾。未有声淫而诗不淫者。桑中溱洧诸篇。自比于乱。岂端人正士之所屑为。夫子所训思无邪者。盖言诗之为教。使人如此。非谓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诗未必尽能无邪。诗之功用。能使读者思无邪。斯论正矣。然史记云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颂之音。则司马氏去古未远。其说岂无所受而然乎哉。况以淫者之自作。而见取于圣人垂世立教之篇。则读之者不惟无以惩创鉴戒。朱子所谓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者。不幸近之。然则此思无邪三字。如何看得然后为通耶。
之郊庙。其释义也。又谓之非美则刺。而虽如郑卫淫奔之诗。亦归之讥讽他人之辞。盖因夫子思无邪之训。而不得不迁就为说也。于是诸儒竞出新解。一则曰声淫而诗不淫。一则曰雅乐郑声。以声乐别。而非以诗别。至朱子一扫诸家。断然以为诗与乐相为首尾。未有声淫而诗不淫者。桑中溱洧诸篇。自比于乱。岂端人正士之所屑为。夫子所训思无邪者。盖言诗之为教。使人如此。非谓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诗未必尽能无邪。诗之功用。能使读者思无邪。斯论正矣。然史记云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颂之音。则司马氏去古未远。其说岂无所受而然乎哉。况以淫者之自作。而见取于圣人垂世立教之篇。则读之者不惟无以惩创鉴戒。朱子所谓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者。不幸近之。然则此思无邪三字。如何看得然后为通耶。宗楷对。诗有止乎礼义者。有不止乎礼义者。如淫奔之诗。淫者之自作。而圣人采之。垂世立教。使读诗者邪正两看。惩彼而兴此。若曰恶人之诗。不当列于正人之诗。则壁经治法之书。而犹载败乱之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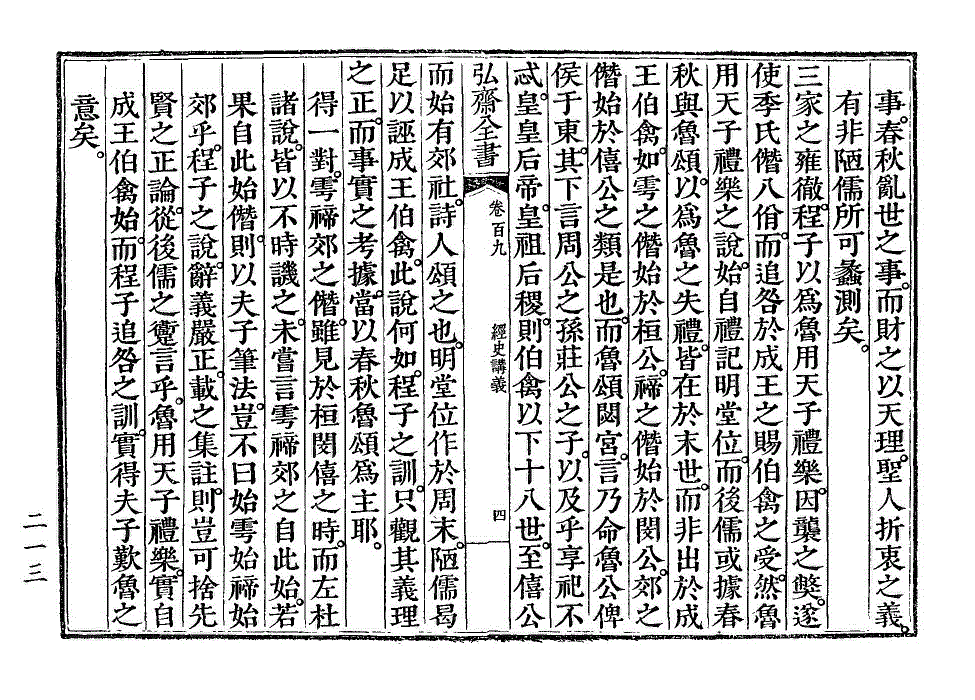 事。春秋乱世之事。而财之以天理。圣人折衷之义。有非陋儒所可蠡测矣。
事。春秋乱世之事。而财之以天理。圣人折衷之义。有非陋儒所可蠡测矣。三家之雍彻。程子以为鲁用天子礼乐。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而追咎于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然鲁用天子礼乐之说。始自礼记明堂位。而后儒或据春秋与鲁颂。以为鲁之失礼。皆在于末世。而非出于成王伯禽。如雩之僭始于桓公。禘之僭始于闵公。郊之僭始于僖公之类是也。而鲁颂閟宫。言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其下言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以及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则伯禽以下十八世。至僖公而始有郊社。诗人颂之也。明堂位作于周末。陋儒曷足以诬成王伯禽。此说何如。程子之训。只观其义理之正。而事实之考据。当以春秋鲁颂为主耶。
得一对。雩禘郊之僭。虽见于桓闵僖之时。而左杜诸说。皆以不时讥之。未尝言雩禘郊之自此始。若果自此始僭。则以夫子笔法。岂不曰始雩始禘始郊乎。程子之说。辞义严正。载之集注。则岂可舍先贤之正论。从后儒之躗言乎。鲁用天子礼乐。实自成王伯禽始。而程子追咎之训。实得夫子叹鲁之意矣。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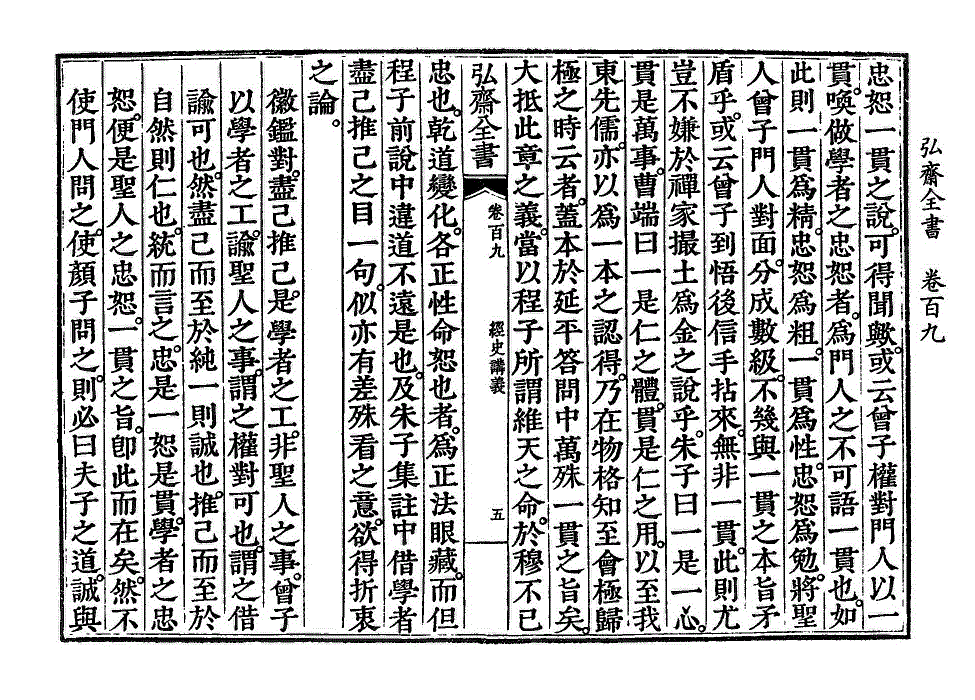 忠恕一贯之说。可得闻欤。或云曾子权对门人以一贯。唤做学者之忠恕者。为门人之不可语一贯也。如此则一贯为精。忠恕为粗。一贯为性。忠恕为勉。将圣人曾子门人对面。分成数级。不几与一贯之本旨矛盾乎。或云曾子到悟后信手拈来。无非一贯。此则尤岂不嫌于禅家撮土为金之说乎。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事。曹端曰一是仁之体。贯是仁之用。以至我东先儒。亦以为一本之认得。乃在物格知至会极归极之时云者。盖本于延平答问中万殊一贯之旨矣。大抵此章之义。当以程子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者。为正法眼藏。而但程子前说中违道不远是也。及朱子集注中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一句。似亦有差殊看之意。欲得折衷之论。
忠恕一贯之说。可得闻欤。或云曾子权对门人以一贯。唤做学者之忠恕者。为门人之不可语一贯也。如此则一贯为精。忠恕为粗。一贯为性。忠恕为勉。将圣人曾子门人对面。分成数级。不几与一贯之本旨矛盾乎。或云曾子到悟后信手拈来。无非一贯。此则尤岂不嫌于禅家撮土为金之说乎。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事。曹端曰一是仁之体。贯是仁之用。以至我东先儒。亦以为一本之认得。乃在物格知至会极归极之时云者。盖本于延平答问中万殊一贯之旨矣。大抵此章之义。当以程子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者。为正法眼藏。而但程子前说中违道不远是也。及朱子集注中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一句。似亦有差殊看之意。欲得折衷之论。徽鉴对。尽己推己。是学者之工。非圣人之事。曾子以学者之工。谕圣人之事。谓之权对可也。谓之借谕可也。然尽己而至于纯一则诚也。推己而至于自然则仁也。统而言之。忠是一恕是贯。学者之忠恕。便是圣人之忠恕。一贯之旨。即此而在矣。然不使门人问之。使颜子问之。则必曰夫子之道。诚与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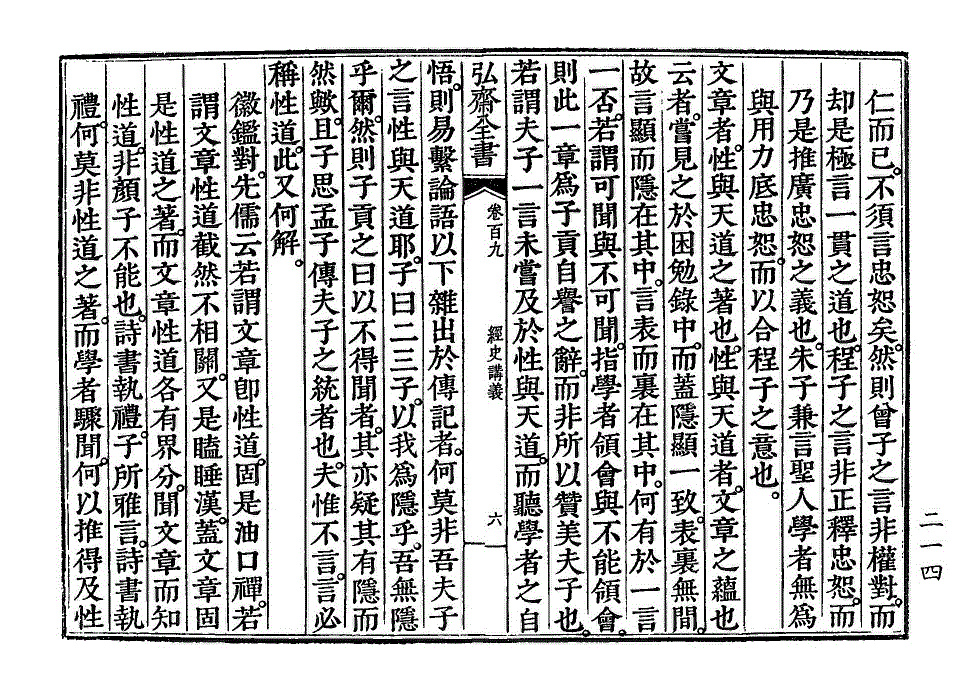 仁而已。不须言忠恕矣。然则曾子之言非权对。而却是极言一贯之道也。程子之言非正释忠恕。而乃是推广忠恕之义也。朱子兼言圣人学者无为与用力底忠恕。而以合程子之意也。
仁而已。不须言忠恕矣。然则曾子之言非权对。而却是极言一贯之道也。程子之言非正释忠恕。而乃是推广忠恕之义也。朱子兼言圣人学者无为与用力底忠恕。而以合程子之意也。文章者。性与天道之著也。性与天道者。文章之蕴也云者。尝见之于困勉录中。而盖隐显一致。表里无间。故言显而隐在其中。言表而里在其中。何有于一言一否。若谓可闻与不可闻。指学者领会与不能领会。则此一章为子贡自誉之辞。而非所以赞美夫子也。若谓夫子一言未尝及于性与天道。而听学者之自悟。则易系论语以下杂出于传记者。何莫非吾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耶。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然则子贡之曰以不得闻者。其亦疑其有隐而然欤。且子思孟子传夫子之统者也。夫惟不言。言必称性道。此又何解。
徽鉴对。先儒云若谓文章即性道。固是油口禅。若谓文章性道截然不相关。又是瞌睡汉。盖文章固是性道之著。而文章性道各有界分。闻文章而知性道。非颜子不能也。诗书执礼。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何莫非性道之著。而学者骤闻。何以推得及性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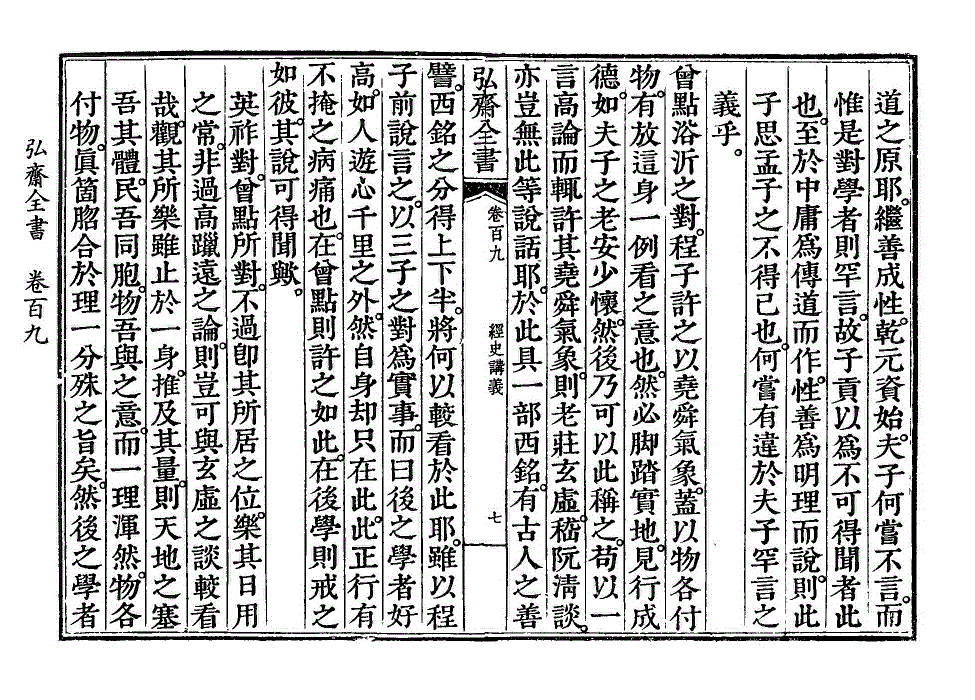 道之原耶。继善成性。乾元资始。夫子何尝不言。而惟是对学者则罕言。故子贡以为不可得闻者此也。至于中庸为传道而作。性善为明理而说。则此子思孟子之不得已也。何尝有违于夫子罕言之义乎。
道之原耶。继善成性。乾元资始。夫子何尝不言。而惟是对学者则罕言。故子贡以为不可得闻者此也。至于中庸为传道而作。性善为明理而说。则此子思孟子之不得已也。何尝有违于夫子罕言之义乎。曾点浴沂之对。程子许之以尧舜气象。盖以物各付物。有放这身一例看之意也。然必脚踏实地。见行成德。如夫子之老安少怀。然后乃可以此称之。苟以一言高论而辄许其尧舜气象。则老庄玄虚。嵇阮清谈。亦岂无此等说话耶。于此具一部西铭。有古人之善譬。西铭之分得上下半。将何以较看于此耶。虽以程子前说言之。以三子之对为实事。而曰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正行有不掩之病痛也。在曾点则许之如此。在后学则戒之如彼。其说可得闻欤。
英祚对。曾点所对。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非过高躐远之论。则岂可与玄虚之谈较看哉。观其所乐虽止于一身。推及其量。则天地之塞吾其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之意。而一理浑然。物各付物。真个吻合于理一分殊之旨矣。然后之学者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5L 页
 无曾点之志。而慕曾点之高。则反不如三子之实事。此程子所以许曾点之气象。戒后学之病痛也。德弘对。古人以西铭譬之棋盘下子。盖无告者也以上属之盘。于时保之以下属之下子。今以此较看乎此章。则天地上下。人己彼此。各得其所。如西铭之上一半。一视同仁。物我无间。如西铭之下一半。吻合之妙。自可见矣。
无曾点之志。而慕曾点之高。则反不如三子之实事。此程子所以许曾点之气象。戒后学之病痛也。德弘对。古人以西铭譬之棋盘下子。盖无告者也以上属之盘。于时保之以下属之下子。今以此较看乎此章。则天地上下。人己彼此。各得其所。如西铭之上一半。一视同仁。物我无间。如西铭之下一半。吻合之妙。自可见矣。先儒以此书。子夏之门人小子章。为朱陆分派之本源。以孟子告子曰生之谓性章。为儒佛分派之本源。此说何如。集注所引程子之说凡五条。而其于本末先后。辨之详矣。但所谓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及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两条。得不太没阶级耶。洒扫应对。小学之始事。精义入神。大学之极功。而圣门之教。贵在循序渐进。不欲躐等陵节。故大学有本末终始知所先后之说。虽以夫子生知之圣。自十五志学。以至七十不踰矩。有十年一进之验矣。程子此说。与此义得不径庭否。我东先儒亦以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不可分本末为两事云尔。则当如何分解。朱子尝为同安簿。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闻子规啼。思量子夏之门人小子章。遂引而不发。盖欲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6H 页
 待人叩问。而惜乎当时门人不复穷其说。使学者用工先后之肯綮。不尽传于后也。愿与诸生讲朱子未发之蕴。
待人叩问。而惜乎当时门人不复穷其说。使学者用工先后之肯綮。不尽传于后也。愿与诸生讲朱子未发之蕴。徽鉴对。子夏只言教有先后之序。不及本末之所以然。故程子极言本末虽殊。其理则一。以明学者不可不循序渐进。亦不可厌末求本之意。实与子夏之言。相为表里。程子之意。岂以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为一项事。亦岂谓只学洒扫应对。便可到尽性知命之域耶。子游所谓本即正心诚意之事。子夏所谓末即洒扫应对之事。子游之讥子夏。非以子夏之末为非。而欲其本末兼治之意也。子夏亦未尝以子游之本为空虚。而专以末为教也。二事同是圣人之道。何关于异端也哉。语类云朱子忽然有觉曰理无大小。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非是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此或是同安以后所论。而发其未尽之义也耶。(以上论语)
[孟子]
经书大指。皆于首章已见之。如易之元亨利贞。书之钦明。诗之关雎。论语之学习。大学之三纲领。中庸之性道教。何莫非关键要领。而孟子首章即仁义与利之辨矣。丘琼山大学衍义补曰入孔子之门者。自孟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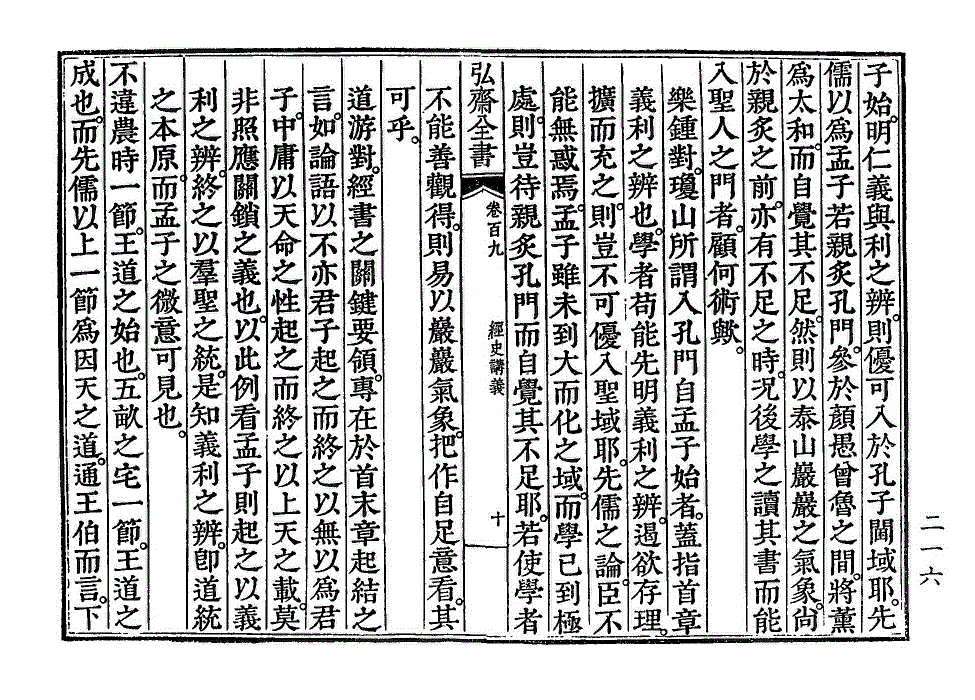 子始。明仁义与利之辨。则优可入于孔子阃域耶。先儒以为孟子若亲炙孔门。参于颜愚曾鲁之间。将薰为太和。而自觉其不足。然则以泰山岩岩之气象。尚于亲炙之前。亦有不足之时。况后学之读其书而能入圣人之门者。顾何术欤。
子始。明仁义与利之辨。则优可入于孔子阃域耶。先儒以为孟子若亲炙孔门。参于颜愚曾鲁之间。将薰为太和。而自觉其不足。然则以泰山岩岩之气象。尚于亲炙之前。亦有不足之时。况后学之读其书而能入圣人之门者。顾何术欤。乐钟对。琼山所谓入孔门自孟子始者。盖指首章义利之辨也。学者苟能先明义利之辨。遏欲存理。扩而充之。则岂不可优入圣域耶。先儒之论。臣不能无惑焉。孟子虽未到大而化之域。而学已到极处。则岂待亲炙孔门而自觉其不足耶。若使学者不能善观得。则易以岩岩气象。把作自足意看。其可乎。
道游对。经书之关键要领。专在于首末章起结之言。如论语以不亦君子起之而终之以无以为君子。中庸以天命之性起之而终之以上天之载。莫非照应关锁之义也。以此例看孟子则起之以义利之辨。终之以群圣之统。是知义利之辨。即道统之本原。而孟子之微意可见也。
不违农时一节。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一节。王道之成也。而先儒以上一节为因天之道。通王伯而言。下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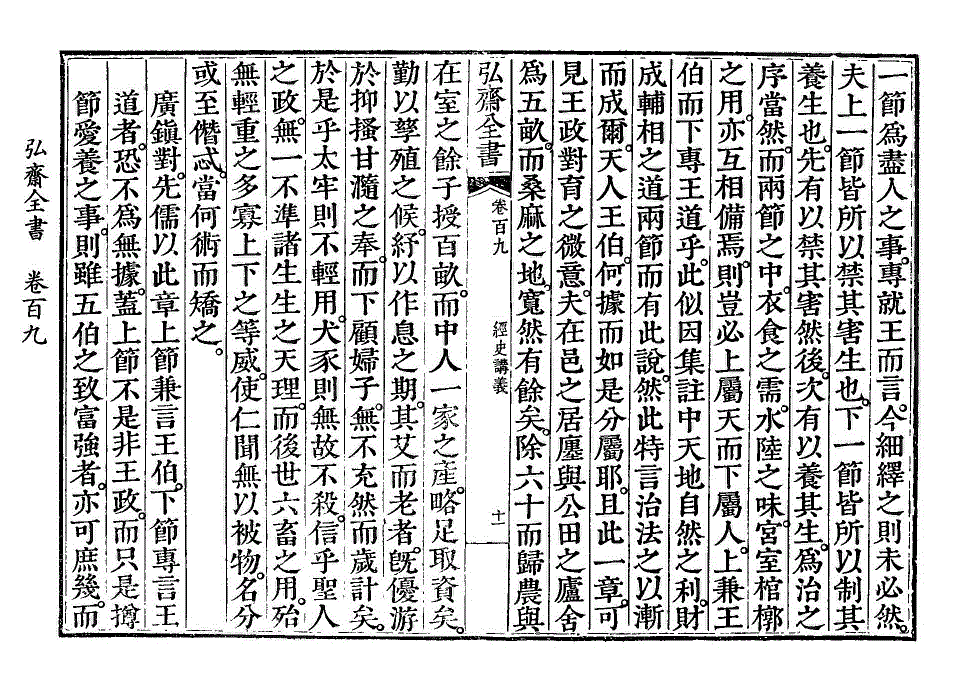 一节为尽人之事。专就王而言。今细绎之则未必然。夫上一节皆所以禁其害生也。下一节皆所以制其养生也。先有以禁其害然后。次有以养其生。为治之序当然。而两节之中。衣食之需。水陆之味。宫室棺椁之用。亦互相备焉。则岂必上属天而下属人。上兼王伯而下专王道乎。此似因集注中天地自然之利。财成辅相之道两节而有此说。然此特言治法之以渐而成尔。天人王伯。何据而如是分属耶。且此一章。可见王政对育之微意。夫在邑之居廛与公田之庐舍为五亩。而桑麻之地。宽然有馀矣。除六十而归农与在室之馀子授百亩。而中人一家之产。略足取资矣。勤以孳殖之候。纾以作息之期。其艾而老者。既优游于抑搔甘瀡之奉。而下顾妇子。无不充然而岁计矣。于是乎太牢则不轻用。犬豕则无故不杀。信乎圣人之政。无一不准诸生生之天理。而后世六畜之用。殆无轻重之多寡上下之等威。使仁闻无以被物。名分或至僭忒。当何术而矫之。
一节为尽人之事。专就王而言。今细绎之则未必然。夫上一节皆所以禁其害生也。下一节皆所以制其养生也。先有以禁其害然后。次有以养其生。为治之序当然。而两节之中。衣食之需。水陆之味。宫室棺椁之用。亦互相备焉。则岂必上属天而下属人。上兼王伯而下专王道乎。此似因集注中天地自然之利。财成辅相之道两节而有此说。然此特言治法之以渐而成尔。天人王伯。何据而如是分属耶。且此一章。可见王政对育之微意。夫在邑之居廛与公田之庐舍为五亩。而桑麻之地。宽然有馀矣。除六十而归农与在室之馀子授百亩。而中人一家之产。略足取资矣。勤以孳殖之候。纾以作息之期。其艾而老者。既优游于抑搔甘瀡之奉。而下顾妇子。无不充然而岁计矣。于是乎太牢则不轻用。犬豕则无故不杀。信乎圣人之政。无一不准诸生生之天理。而后世六畜之用。殆无轻重之多寡上下之等威。使仁闻无以被物。名分或至僭忒。当何术而矫之。广镇对。先儒以此章上节兼言王伯。下节专言王道者。恐不为无据。盖上节不是非王政。而只是撙节爱养之事。则虽五伯之致富强者。亦可庶几。而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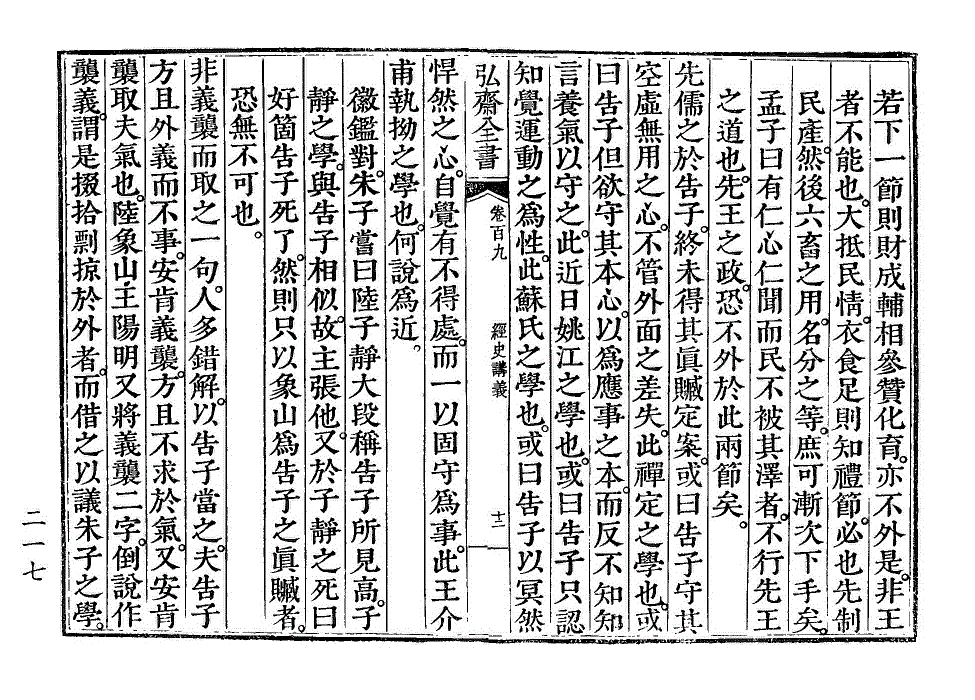 若下一节则财成辅相参赞化育。亦不外是。非王者不能也。大抵民情。衣食足则知礼节。必也先制民产。然后六畜之用。名分之等。庶可渐次下手矣。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政。恐不外于此两节矣。
若下一节则财成辅相参赞化育。亦不外是。非王者不能也。大抵民情。衣食足则知礼节。必也先制民产。然后六畜之用。名分之等。庶可渐次下手矣。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政。恐不外于此两节矣。先儒之于告子。终未得其真赃定案。或曰告子守其空虚无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此禅定之学也。或曰告子但欲守其本心。以为应事之本。而反不知知言养气以守之。此近日姚江之学也。或曰告子只认知觉运动之为性。此苏氏之学也。或曰告子以冥然悍然之心。自觉有不得处。而一以固守为事。此王介甫执拗之学也。何说为近。
徽鉴对。朱子尝曰陆子静大段称告子所见高。子静之学。与告子相似。故主张他。又于子静之死曰好个告子死了。然则只以象山为告子之真赃者。恐无不可也。
非义袭而取之一句。人多错解。以告子当之。夫告子方且外义而不事。安肯义袭。方且不求于气。又安肯袭取夫气也。陆象,山王阳明又将义袭二字。倒说作袭义。谓是掇拾剽掠于外者。而借之以议朱子之学。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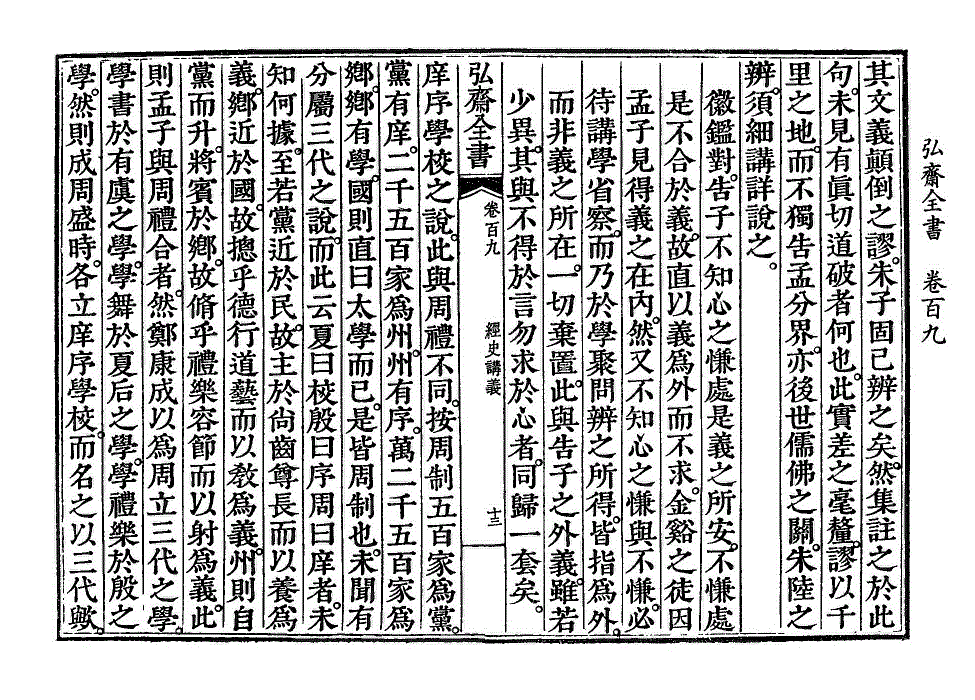 其文义颠倒之谬。朱子固已辨之矣。然集注之于此句。未见有真切道破者何也。此实差之毫釐。谬以千里之地。而不独告孟分界。亦后世儒佛之关。朱陆之辨。须细讲详说之。
其文义颠倒之谬。朱子固已辨之矣。然集注之于此句。未见有真切道破者何也。此实差之毫釐。谬以千里之地。而不独告孟分界。亦后世儒佛之关。朱陆之辨。须细讲详说之。徽鉴对。告子不知心之慊处是义之所安。不慊处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金溪之徒因孟子见得义之在内。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必待讲学省察。而乃于学聚问辨之所得。皆指为外。而非义之所在。一切弃置。此与告子之外义。虽若少异。其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同归一套矣。
庠序学校之说。此与周礼不同。按周制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序。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学。国则直曰太学而已。是皆周制也。未闻有分属三代之说。而此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未知何据。至若党近于民。故主于尚齿尊长而以养为义。乡近于国。故总乎德行道艺而以教为义。州则自党而升。将宾于乡。故脩乎礼乐容节而以射为义。此则孟子与周礼合者。然郑康成以为周立三代之学。学书于有虞之学。学舞于夏后之学。学礼乐于殷之学。然则成周盛时。各立庠序学校。而名之以三代欤。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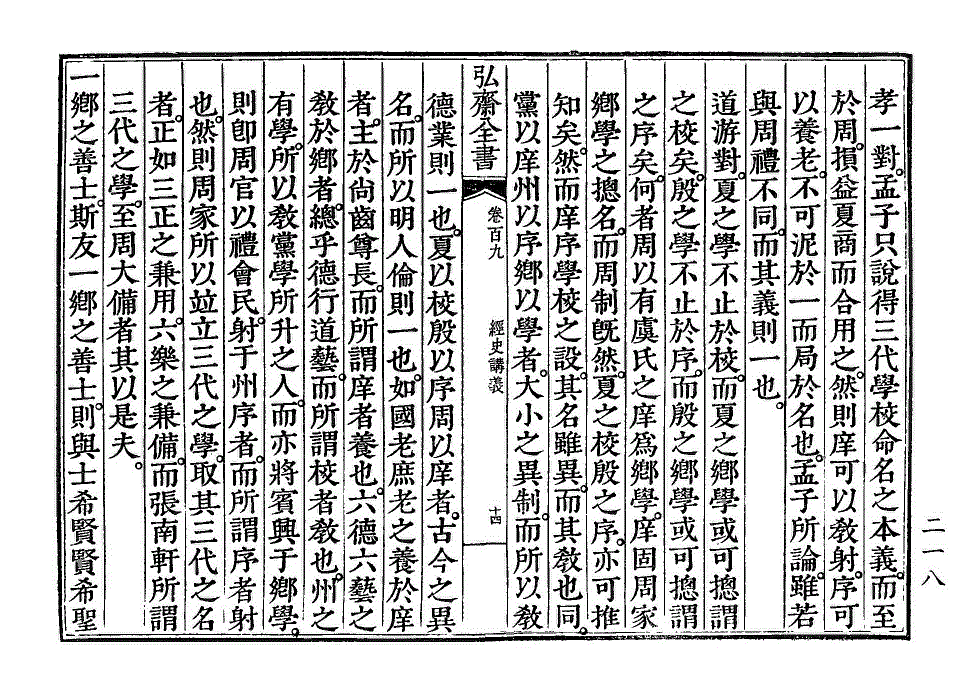 孝一对。孟子只说得三代学校命名之本义。而至于周。损益夏商而合用之。然则庠可以教射。序可以养老。不可泥于一而局于名也。孟子所论。虽若与周礼不同。而其义则一也。
孝一对。孟子只说得三代学校命名之本义。而至于周。损益夏商而合用之。然则庠可以教射。序可以养老。不可泥于一而局于名也。孟子所论。虽若与周礼不同。而其义则一也。道游对。夏之学不止于校。而夏之乡学或可总谓之校矣。殷之学不止于序。而殷之乡学或可总谓之序矣。何者周以有虞氏之庠为乡学。庠固周家乡学之总名。而周制既然。夏之校殷之序。亦可推知矣。然而庠序学校之设。其名虽异。而其教也同。党以庠州以序乡以学者。大小之异制。而所以教德业则一也。夏以校殷以序周以庠者。古今之异名。而所以明人伦则一也。如国老庶老之养于庠者。主于尚齿尊长。而所谓庠者养也。六德六艺之教于乡者。总乎德行道艺。而所谓校者教也。州之有学。所以教党学所升之人。而亦将宾兴于乡学。则即周官以礼会民。射于州序者。而所谓序者射也。然则周家所以并立三代之学。取其三代之名者。正如三正之兼用。六乐之兼备。而张南轩所谓三代之学。至周大备者其以是夫。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则与士希贤贤希圣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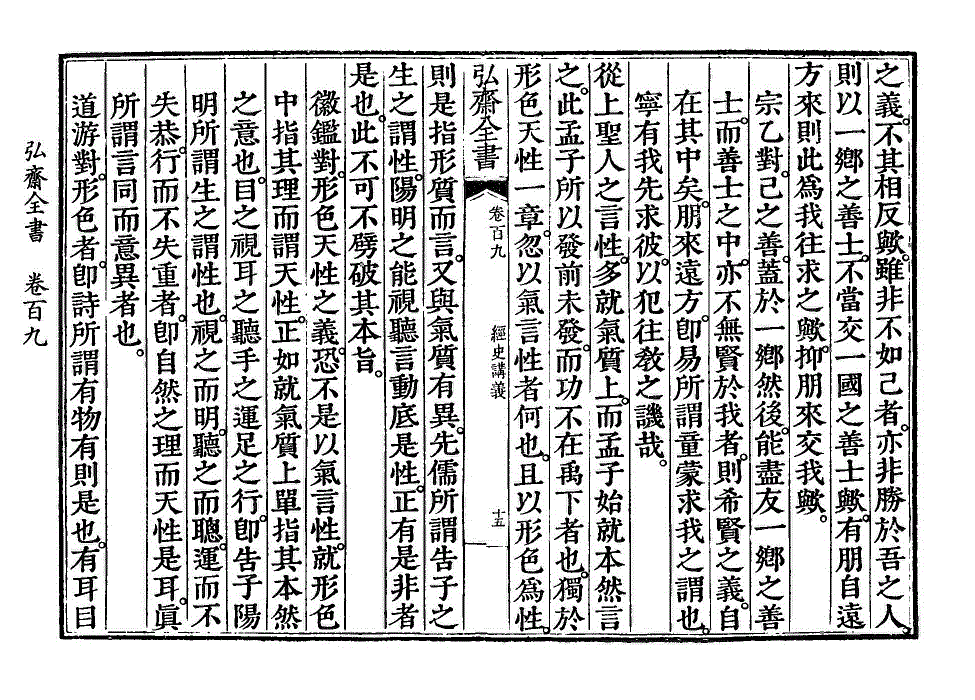 之义。不其相反欤。虽非不如己者。亦非胜于吾之人。则以一乡之善士。不当交一国之善士欤。有朋自远方来则此为我往求之欤。抑朋来交我欤。
之义。不其相反欤。虽非不如己者。亦非胜于吾之人。则以一乡之善士。不当交一国之善士欤。有朋自远方来则此为我往求之欤。抑朋来交我欤。宗乙对。己之善。盖于一乡然后。能尽友一乡之善士。而善士之中。亦不无贤于我者。则希贤之义。自在其中矣。朋来远方。即易所谓童蒙求我之谓也。宁有我先求彼。以犯往教之讥哉。
从上圣人之言性。多就气质上。而孟子始就本然言之。此孟子所以发前未发。而功不在禹下者也。独于形色天性一章。忽以气言性者何也。且以形色为性。则是指形质而言。又与气质有异。先儒所谓告子之生之谓性。阳明之能视听言动底是性。正有是非者是也。此不可不劈破其本旨。
徽鉴对。形色天性之义。恐不是以气言性。就形色中指其理而谓天性。正如就气质上单指其本然之意也。目之视耳之听手之运足之行。即告子阳明所谓生之谓性也。视之而明。听之而聪。运而不失恭。行而不失重者。即自然之理而天性是耳。真所谓言同而意异者也。
道游对。形色者。即诗所谓有物有则是也。有耳目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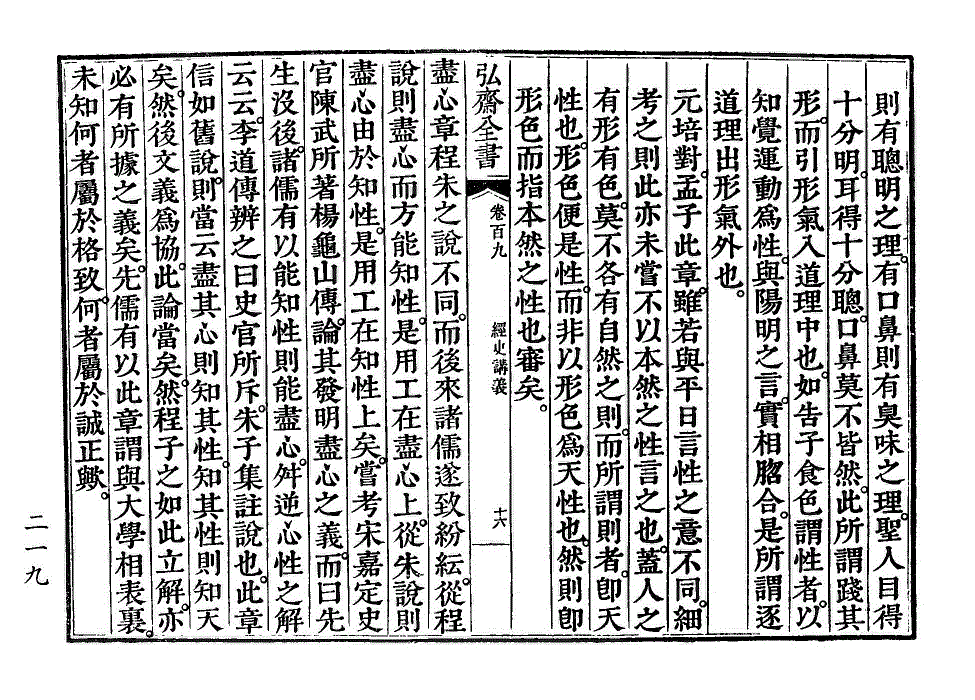 则有聪明之理。有口鼻则有臭味之理。圣人目得十分明。耳得十分聪。口鼻莫不皆然。此所谓践其形。而引形气入道理中也。如告子食色谓性者。以知觉运动为性。与阳明之言。实相吻合。是所谓逐道理出形气外也。
则有聪明之理。有口鼻则有臭味之理。圣人目得十分明。耳得十分聪。口鼻莫不皆然。此所谓践其形。而引形气入道理中也。如告子食色谓性者。以知觉运动为性。与阳明之言。实相吻合。是所谓逐道理出形气外也。元培对。孟子此章。虽若与平日言性之意不同。细考之则此亦未尝不以本然之性言之也。盖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则。而所谓则者。即天性也。形色便是性。而非以形色为天性也。然则即形色而指本然之性也审矣。
尽心章程朱之说不同。而后来诸儒遂致纷纭。从程说则尽心而方能知性。是用工在尽心上。从朱说则尽心由于知性。是用工在知性上矣。尝考宋嘉定史官陈武所著杨龟山传。论其发明尽心之义。而曰先生没后。诸儒有以能知性则能尽心。舛逆心性之解云云。李道传辨之曰史官所斥。朱子集注说也。此章信如旧说。则当云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然后文义为协。此论当矣。然程子之如此立解。亦必有所据之义矣。先儒有以此章谓与大学相表里。未知何者属于格致。何者属于诚正欤。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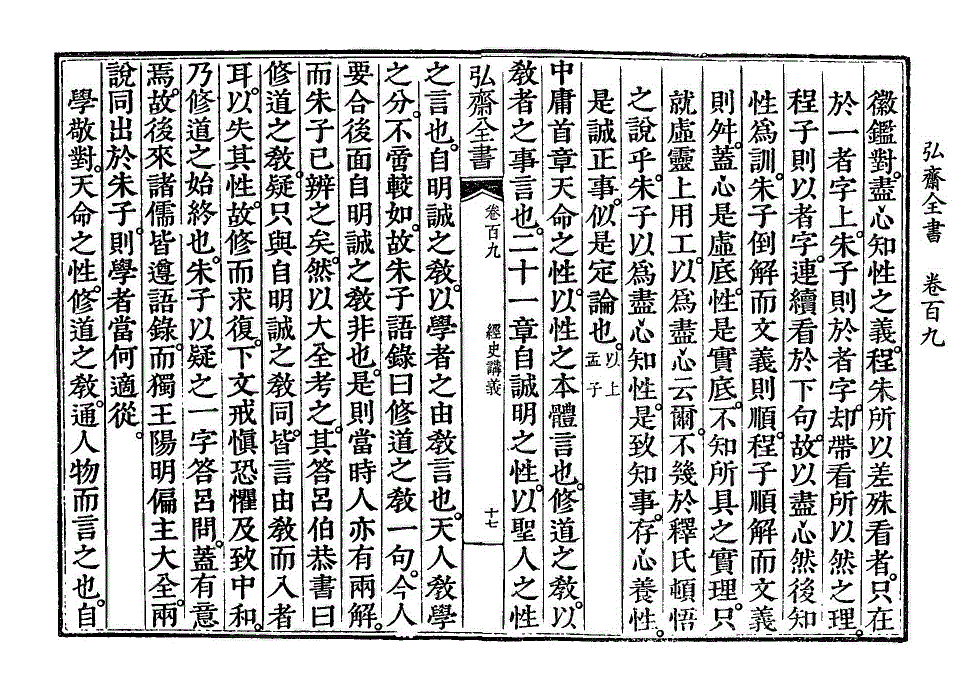 徽鉴对。尽心知性之义。程朱所以差殊看者。只在于一者字上。朱子则于者字。却带看所以然之理。程子则以者字。连续看于下句。故以尽心然后知性为训。朱子倒解而文义则顺。程子顺解而文义则舛。盖心是虚底。性是实底。不知所具之实理。只就虚灵上用工。以为尽心云尔。不几于释氏顿悟之说乎。朱子以为尽心知性。是致知事。存心养性。是诚正事。似是定论也。(以上孟子)
徽鉴对。尽心知性之义。程朱所以差殊看者。只在于一者字上。朱子则于者字。却带看所以然之理。程子则以者字。连续看于下句。故以尽心然后知性为训。朱子倒解而文义则顺。程子顺解而文义则舛。盖心是虚底。性是实底。不知所具之实理。只就虚灵上用工。以为尽心云尔。不几于释氏顿悟之说乎。朱子以为尽心知性。是致知事。存心养性。是诚正事。似是定论也。(以上孟子)[中庸]
中庸首章天命之性。以性之本体言也。修道之教。以教者之事言也。二十一章自诚明之性。以圣人之性之言也。自明诚之教。以学者之由教言也。天人教学之分。不啻较如。故朱子语录曰修道之教一句。今人要合后面自明诚之教非也。是则当时人亦有两解。而朱子已辨之矣。然以大全考之。其答吕伯恭书曰修道之教。疑只与自明诚之教同。皆言由教而入者耳。以失其性。故修而求复。下文戒慎恐惧及致中和。乃修道之始终也。朱子以疑之一字答吕问。盖有意焉。故后来诸儒皆遵语录。而独王阳明偏主大全。两说同出于朱子。则学者当何适从。
学敬对。天命之性。修道之教。通人物而言之也。自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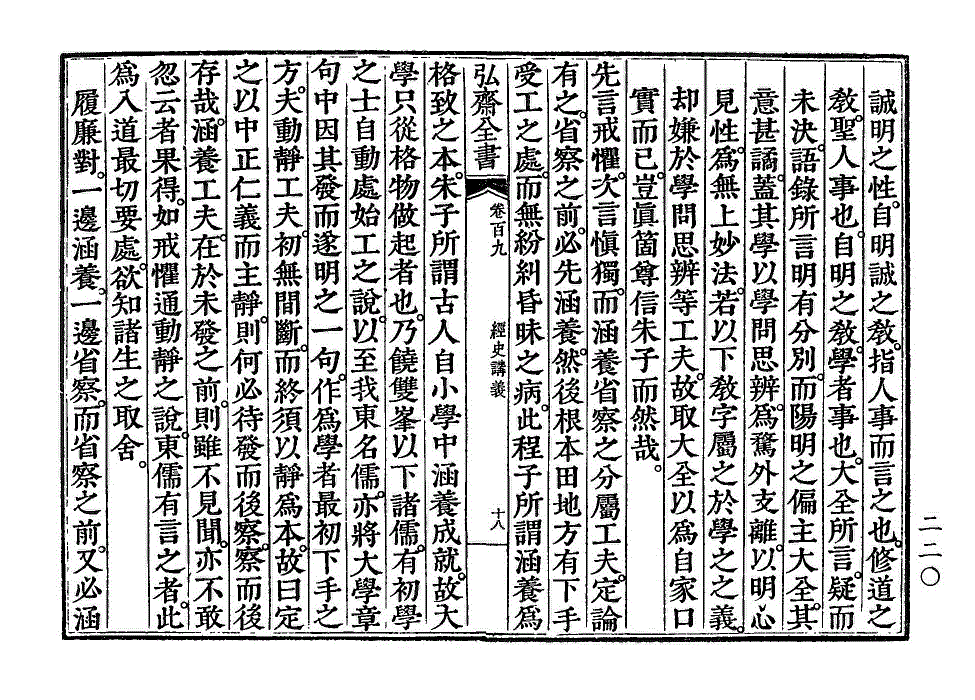 诚明之性。自明诚之教。指人事而言之也。修道之教。圣人事也。自明之教。学者事也。大全所言。疑而未决。语录所言明有分别。而阳明之偏主大全。其意甚谲。盖其学以学问思辨。为骛外支离。以明心见性。为无上妙法。若以下教字属之于学之之义。却嫌于学问思辨等工夫。故取大全以为自家口实而已。岂真个尊信朱子而然哉。
诚明之性。自明诚之教。指人事而言之也。修道之教。圣人事也。自明之教。学者事也。大全所言。疑而未决。语录所言明有分别。而阳明之偏主大全。其意甚谲。盖其学以学问思辨。为骛外支离。以明心见性。为无上妙法。若以下教字属之于学之之义。却嫌于学问思辨等工夫。故取大全以为自家口实而已。岂真个尊信朱子而然哉。先言戒惧。次言慎独。而涵养省察之分属工夫。定论有之。省察之前。必先涵养。然后根本田地方有下手受工之处。而无纷纠昏昧之病。此程子所谓涵养为格致之本。朱子所谓古人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故大学只从格物做起者也。乃饶双峰以下诸儒。有初学之士自动处始工之说。以至我东名儒。亦将大学章句中因其发而遂明之一句。作为学者最初下手之方。夫动静工夫。初无间断。而终须以静为本。故曰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则何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哉。涵养工夫。在于未发之前。则虽不见闻。亦不敢忽云者果得。如戒惧通动静之说。东儒有言之者。此为入道最切要处。欲知诸生之取舍。
履廉对。一边涵养。一边省察。而省察之前。又必涵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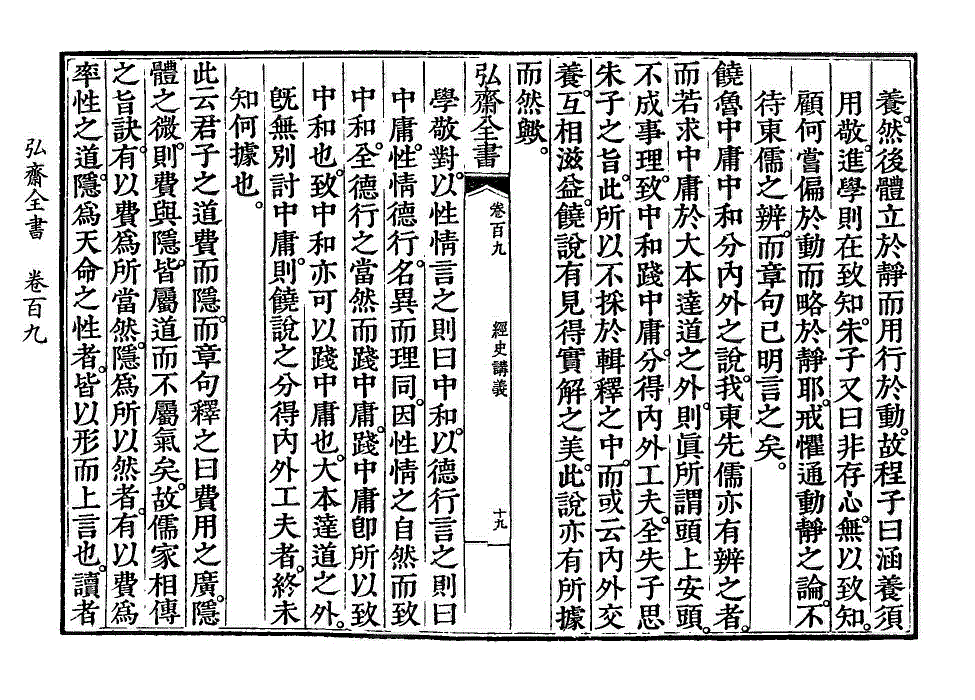 养。然后体立于静而用行于动。故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又曰非存心。无以致知。顾何尝偏于动而略于静耶。戒惧通动静之论。不待东儒之辨。而章句已明言之矣。
养。然后体立于静而用行于动。故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又曰非存心。无以致知。顾何尝偏于动而略于静耶。戒惧通动静之论。不待东儒之辨。而章句已明言之矣。饶鲁中庸中和分内外之说。我东先儒亦有辨之者。而若求中庸于大本达道之外。则真所谓头上安头。不成事理。致中和践中庸。分得内外工夫。全失子思朱子之旨。此所以不采于辑释之中。而或云内外交养。互相滋益。饶说有见得实解之美。此说亦有所据而然欤。
学敬对。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性情德行。名异而理同。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全德行之当然而践中庸。践中庸即所以致中和也。致中和亦可以践中庸也。大本达道之外。既无别讨中庸。则饶说之分得内外工夫者。终未知何据也。
此云君子之道费而隐。而章句释之曰费用之广。隐体之微。则费与隐。皆属道而不属气矣。故儒家相传之旨诀。有以费为所当然。隐为所以然者。有以费为率性之道。隐为天命之性者。皆以形而上言也。读者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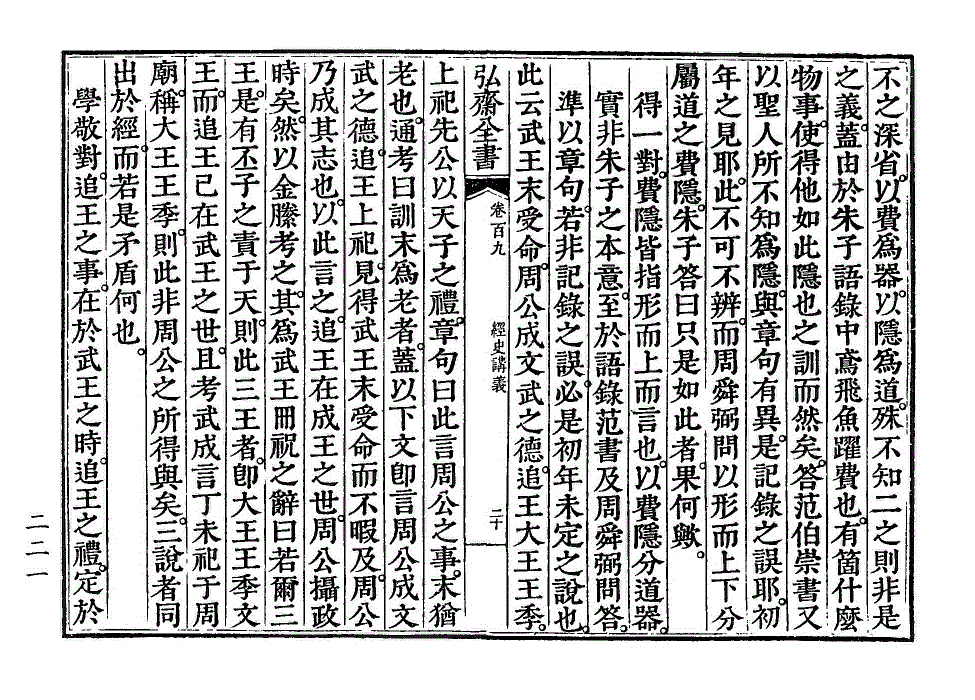 不之深省。以费为器。以隐为道。殊不知二之则非是之义。盖由于朱子语录中鸢飞鱼跃费也。有个什么物事。使得他如此隐也之训而然矣。答范伯崇书又以圣人所不知为隐。与章句有异。是记录之误耶。初年之见耶。此不可不辨。而周舜弼问以形而上下分属道之费隐。朱子答曰只是如此者。果何欤。
不之深省。以费为器。以隐为道。殊不知二之则非是之义。盖由于朱子语录中鸢飞鱼跃费也。有个什么物事。使得他如此隐也之训而然矣。答范伯崇书又以圣人所不知为隐。与章句有异。是记录之误耶。初年之见耶。此不可不辨。而周舜弼问以形而上下分属道之费隐。朱子答曰只是如此者。果何欤。得一对。费隐皆指形而上而言也。以费隐分道器。实非朱子之本意。至于语录范书及周舜弼问答。准以章句。若非记录之误。必是初年未定之说也。
此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章句曰此言周公之事。末犹老也。通考曰训末为老者。盖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见得武王末受命而不暇及。周公乃成其志也。以此言之。追王在成王之世。周公摄政时矣。然以金縢考之。其为武王册祝之辞曰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则此三王者。即大王王季文王。而追王已在武王之世。且考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称大王王季。则此非周公之所得与矣。三说者同出于经。而若是矛盾何也。
学敬对。追王之事。在于武王之时。追王之礼。定于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2H 页
 周公之制。武王受命为天子。享国七年。则追王大礼。缘何未行于七年之内乎。然则武王之追王。固无可疑。而特其王者礼制则至周公相成王后大备也。朱子尝曰武王时恐且呼唤作王。至周公制礼乐。方行其事。如今奉册宝之礼也。似是的论也。
周公之制。武王受命为天子。享国七年。则追王大礼。缘何未行于七年之内乎。然则武王之追王。固无可疑。而特其王者礼制则至周公相成王后大备也。朱子尝曰武王时恐且呼唤作王。至周公制礼乐。方行其事。如今奉册宝之礼也。似是的论也。尊德性道问学一节。读者每惑于知行之分。而以章句之属于存心与致知。又疑其漏却力行。遂以力行归之存心。胡炳文辨之得矣。若以力行属于致知则亦矫过之失矣。然纷若聚讼。尚未一定。当如何晓得。可息诸说。
徽鉴对。为学之道。不出于知行两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既属于知。则上五句不属行边而更属何处乎。以存心为力行云者。固可谓不知心与事之别。而若以存心属于行外则亦非通贯内外之道也。(以上中庸)
[大学]
大学经一章后经之先而又先。即前经三在之倒说也。后经之后而又后。即前经四能之竖说也。后经之治乱厚薄。即前经本末终始之照应也。三纲八目。条贯秩然。若经若传。未曾有一字之变幻。而独于逆推工夫。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不曰欲致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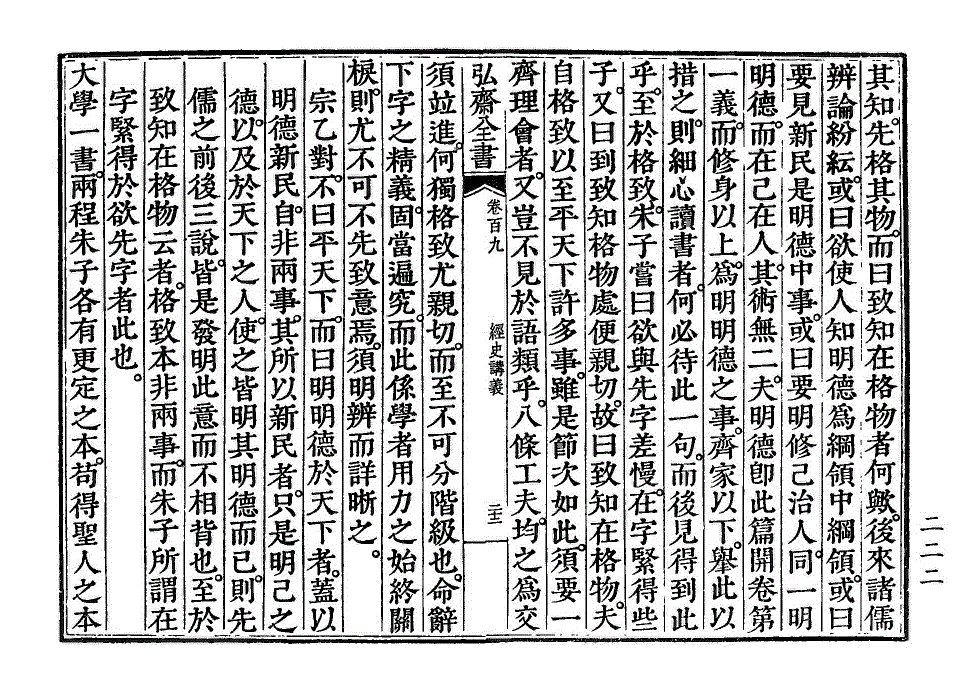 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者何欤。后来诸儒辨论纷纭。或曰欲使人知明德为纲领中纲领。或曰要见新民是明德中事。或曰要明修己治人。同一明明德。而在己在人。其术无二。夫明德即此篇开卷第一义。而修身以上。为明明德之事。齐家以下。举此以措之。则细心读书者。何必待此一句。而后见得到此乎。至于格致。朱子尝曰欲与先字差慢。在字紧得些子。又曰到致知格物处便亲切。故曰致知在格物。夫自格致以至平天下许多事。虽是节次如此。须要一齐理会者。又岂不见于语类乎。八条工夫。均之为交须并进。何独格致尤亲切。而至不可分阶级也。命辞下字之精义。固当遍究。而此系学者用力之始终关棙。则尤不可不先致意焉。须明辨而详晰之。
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者何欤。后来诸儒辨论纷纭。或曰欲使人知明德为纲领中纲领。或曰要见新民是明德中事。或曰要明修己治人。同一明明德。而在己在人。其术无二。夫明德即此篇开卷第一义。而修身以上。为明明德之事。齐家以下。举此以措之。则细心读书者。何必待此一句。而后见得到此乎。至于格致。朱子尝曰欲与先字差慢。在字紧得些子。又曰到致知格物处便亲切。故曰致知在格物。夫自格致以至平天下许多事。虽是节次如此。须要一齐理会者。又岂不见于语类乎。八条工夫。均之为交须并进。何独格致尤亲切。而至不可分阶级也。命辞下字之精义。固当遍究。而此系学者用力之始终关棙。则尤不可不先致意焉。须明辨而详晰之。宗乙对。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盖以明德新民。自非两事。其所以新民者。只是明己之德。以及于天下之人。使之皆明其明德而已。则先儒之前后三说。皆是发明此意而不相背也。至于致知在格物云者。格致本非两事。而朱子所谓在字紧得于欲先字者此也。
大学一书。两程朱子各有更定之本。苟得圣人之本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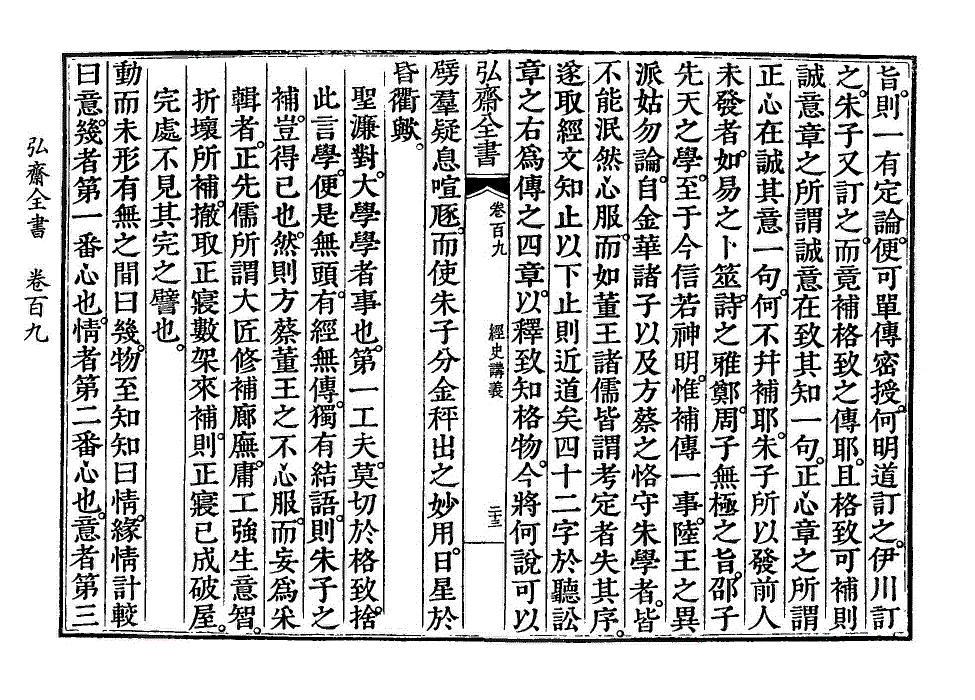 旨。则一有定论。便可单传密授。何明道订之。伊川订之。朱子又订之。而竟补格致之传耶。且格致可补则诚意章之所谓诚意在致其知一句。正心章之所谓正心在诚其意一句。何不并补耶。朱子所以发前人未发者。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学。至于今信若神明。惟补传一事。陆王之异派姑勿论。自金华诸子以及方蔡之恪守朱学者。皆不能泯然心服。而如董王诸儒皆谓考定者失其序。遂取经文知止以下止则近道矣四十二字于听讼章之右为传之四章。以释致知格物。今将何说可以劈群疑息喧豗。而使朱子分金秤出之妙用。日星于昏衢欤。
旨。则一有定论。便可单传密授。何明道订之。伊川订之。朱子又订之。而竟补格致之传耶。且格致可补则诚意章之所谓诚意在致其知一句。正心章之所谓正心在诚其意一句。何不并补耶。朱子所以发前人未发者。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学。至于今信若神明。惟补传一事。陆王之异派姑勿论。自金华诸子以及方蔡之恪守朱学者。皆不能泯然心服。而如董王诸儒皆谓考定者失其序。遂取经文知止以下止则近道矣四十二字于听讼章之右为传之四章。以释致知格物。今将何说可以劈群疑息喧豗。而使朱子分金秤出之妙用。日星于昏衢欤。圣濂对。大学学者事也。第一工夫。莫切于格致。舍此言学。便是无头。有经无传。独有结语。则朱子之补。岂得已也。然则方蔡董王之不心服。而妄为采辑者。正先儒所谓大匠修补廊庑。庸工强生意智。折坏所补。撤取正寝数架来补。则正寝已成破屋。完处不见其完之譬也。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曰几。物至知知曰情。缘情计较曰意。几者第一番心也。情者第二番心也。意者第三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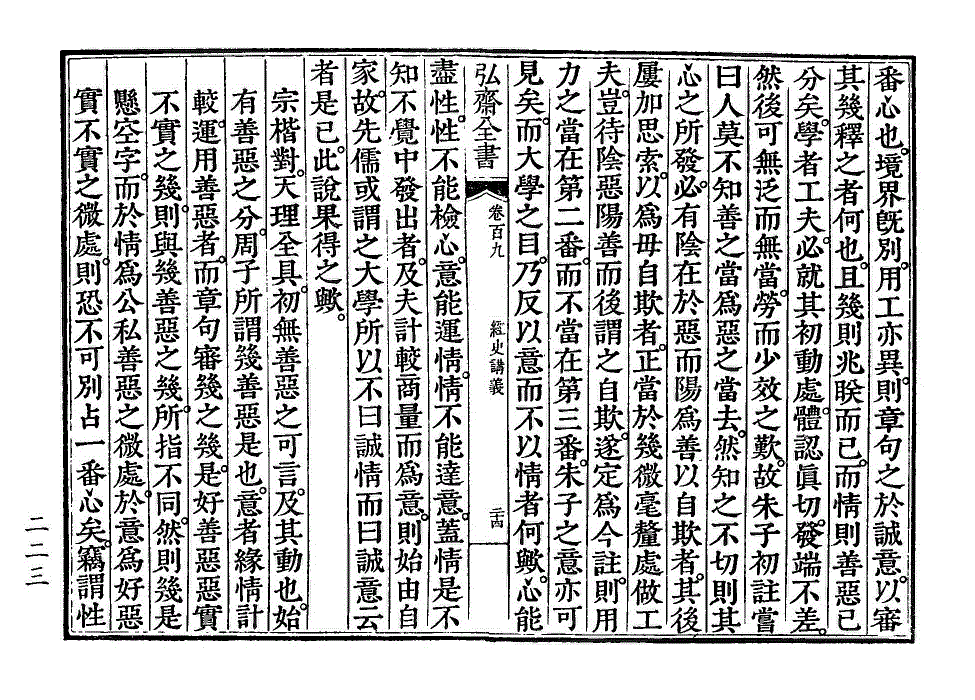 番心也。境界既别。用工亦异。则章句之于诚意。以审其几释之者何也。且几则兆眹而已。而情则善恶已分矣。学者工夫。必就其初动处。体认真切。发端不差。然后可无泛而无当。劳而少效之叹。故朱子初注尝曰人莫不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其后屡加思索。以为毋自欺者。正当于几微毫釐处做工夫。岂待阴恶阳善而后谓之自欺。遂定为今注。则用力之当在第二番。而不当在第三番。朱子之意亦可见矣。而大学之目。乃反以意而不以情者何欤。心能尽性。性不能检心。意能运情。情不能达意。盖情是不知不觉中发出者。及夫计较商量而为意。则始由自家。故先儒或谓之大学所以不曰诚情而曰诚意云者是已。此说果得之欤。
番心也。境界既别。用工亦异。则章句之于诚意。以审其几释之者何也。且几则兆眹而已。而情则善恶已分矣。学者工夫。必就其初动处。体认真切。发端不差。然后可无泛而无当。劳而少效之叹。故朱子初注尝曰人莫不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其后屡加思索。以为毋自欺者。正当于几微毫釐处做工夫。岂待阴恶阳善而后谓之自欺。遂定为今注。则用力之当在第二番。而不当在第三番。朱子之意亦可见矣。而大学之目。乃反以意而不以情者何欤。心能尽性。性不能检心。意能运情。情不能达意。盖情是不知不觉中发出者。及夫计较商量而为意。则始由自家。故先儒或谓之大学所以不曰诚情而曰诚意云者是已。此说果得之欤。宗楷对。天理全具。初无善恶之可言。及其动也。始有善恶之分。周子所谓几善恶是也。意者缘情计较。运用善恶者。而章句审几之几。是好善恶恶实不实之几。则与几善恶之几。所指不同。然则几是悬空字。而于情为公私善恶之微处。于意为好恶实不实之微处。则恐不可别占一番心矣。窃谓性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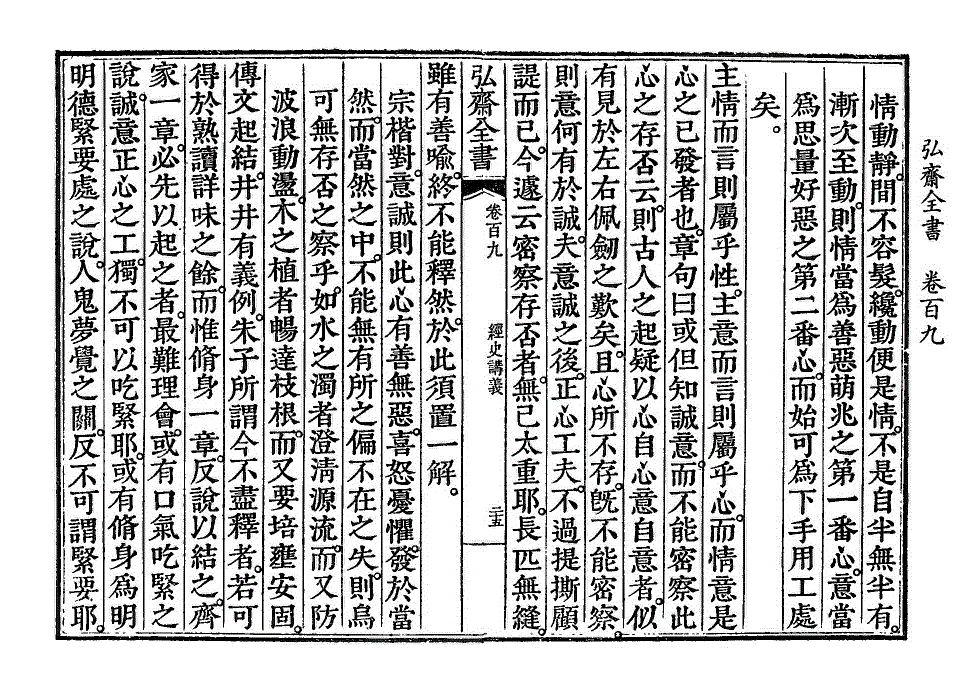 情动静。间不容发。才动便是情。不是自半无半有。渐次至动。则情当为善恶萌兆之第一番心。意当为思量好恶之第二番心。而始可为下手用工处矣。
情动静。间不容发。才动便是情。不是自半无半有。渐次至动。则情当为善恶萌兆之第一番心。意当为思量好恶之第二番心。而始可为下手用工处矣。主情而言则属乎性。主意而言则属乎心。而情意是心之已发者也。章句曰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云。则古人之起疑以心自心意自意者。似有见于左右佩剑之叹矣。且心所不存。既不能密察。则意何有于诚。夫意诚之后。正心工夫。不过提撕顾諟而已。今遽云密察存否者。无已太重耶。长匹无缝。虽有善喻。终不能释然。于此须置一解。
宗楷对。意诚则此心有善无恶。喜怒忧惧。发于当然。而当然之中。不能无有所之偏不在之失。则乌可无存否之察乎。如水之浊者澄清源流。而又防波浪动荡。木之植者畅达枝根。而又要培壅安固。
传文起结。井井有义例。朱子所谓今不尽释者。若可得于熟读详味之馀。而惟脩身一章。反说以结之。齐家一章。必先以起之者。最难理会。或有口气吃紧之说。诚意正心之工。独不可以吃紧耶。或有脩身为明明德紧要处之说。人鬼梦觉之关。反不可谓紧要耶。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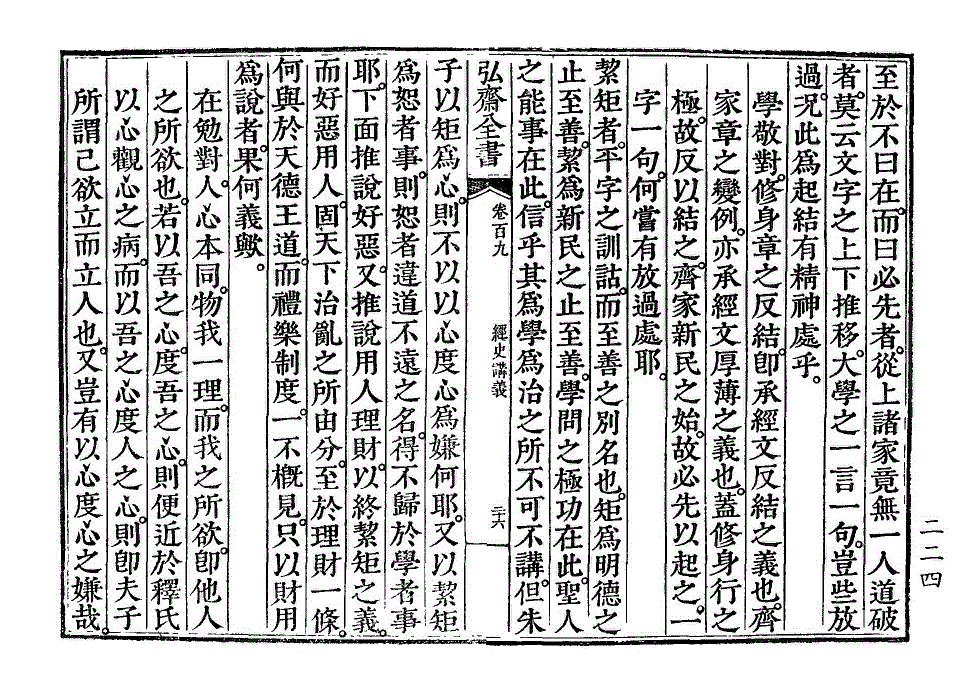 至于不曰在。而曰必先者。从上诸家竟无一人道破者。莫云文字之上下推移。大学之一言一句。岂些放过。况此为起结有精神处乎。
至于不曰在。而曰必先者。从上诸家竟无一人道破者。莫云文字之上下推移。大学之一言一句。岂些放过。况此为起结有精神处乎。学敬对。修身章之反结。即承经文反结之义也。齐家章之变例。亦承经文厚薄之义也。盖修身行之极。故反以结之。齐家新民之始。故必先以起之。一字一句。何尝有放过处耶。
絜矩者。平字之训诂。而至善之别名也。矩为明德之止至善。絜为新民之止至善。学问之极功在此。圣人之能事在此。信乎其为学为治之所不可不讲。但朱子以矩为心。则不以以心度心为嫌何耶。又以絜矩为恕者事。则恕者违道不远之名。得不归于学者事耶。下面推说好恶。又推说用人理财。以终絜矩之义。而好恶用人。固天下治乱之所由分。至于理财一条。何与于天德王道。而礼乐制度。一不概见。只以财用为说者。果何义欤。
在勉对。人心本同。物我一理。而我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若以吾之心。度吾之心。则便近于释氏以心观心之病。而以吾之心度人之心。则即夫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也。又岂有以心度心之嫌哉。
弘斋全书卷百九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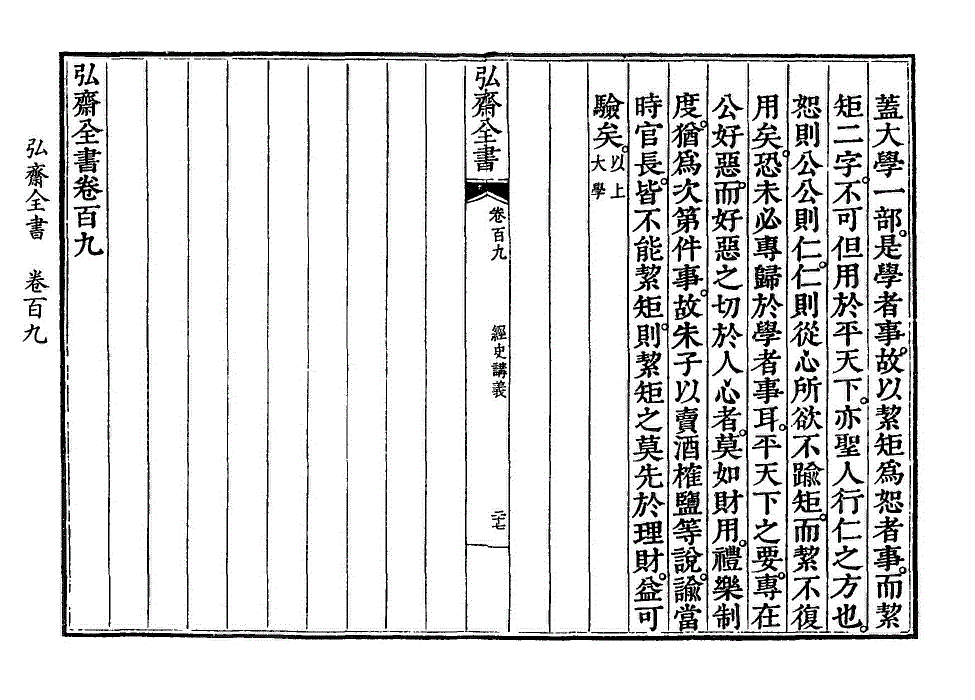 盖大学一部。是学者事。故以絜矩为恕者事。而絜矩二字。不可但用于平天下。亦圣人行仁之方也。恕则公公则仁。仁则从心所欲不踰矩。而絜不复用矣。恐未必专归于学者事耳。平天下之要。专在公好恶。而好恶之切于人心者。莫如财用。礼乐制度。犹为次第件事。故朱子以卖酒榷盐等说。谕当时官长。皆不能絜矩。则絜矩之莫先于理财。益可验矣。(以上大学)
盖大学一部。是学者事。故以絜矩为恕者事。而絜矩二字。不可但用于平天下。亦圣人行仁之方也。恕则公公则仁。仁则从心所欲不踰矩。而絜不复用矣。恐未必专归于学者事耳。平天下之要。专在公好恶。而好恶之切于人心者。莫如财用。礼乐制度。犹为次第件事。故朱子以卖酒榷盐等说。谕当时官长。皆不能絜矩。则絜矩之莫先于理财。益可验矣。(以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