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x 页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明皋徐滢修汝琳 著)
[洪范直指]
[洪范直指]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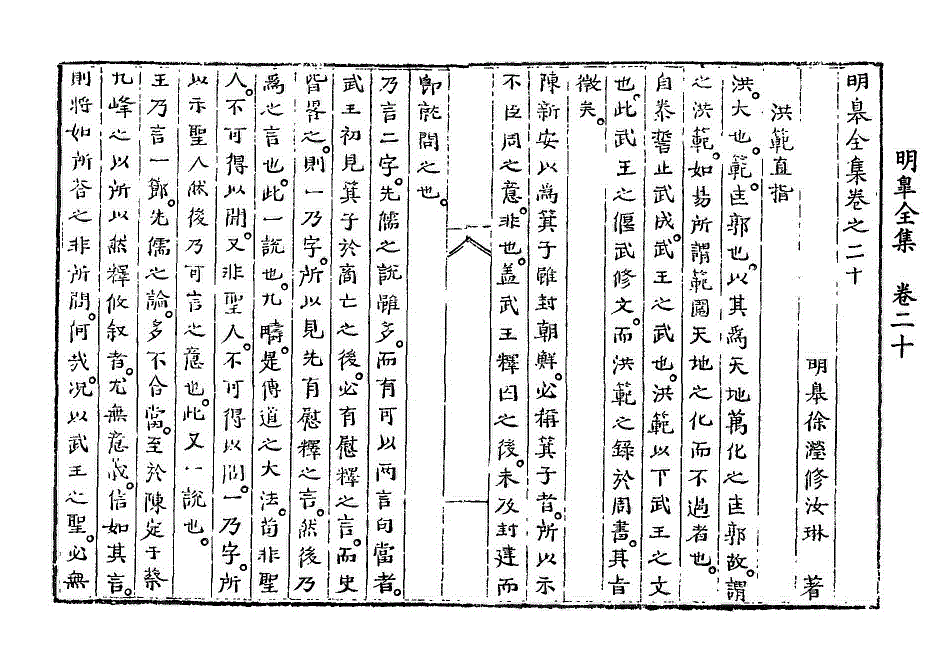 洪范直指
洪范直指洪。大也。范。匡郭也。以其为天地万化之匡郭故。谓之洪范。如易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者也。
自泰誓止武成。武王之武也。洪范以下武王之文也。此武王之偃武修文。而洪范之录于周书。其旨微矣。
陈新安以为箕子虽封朝鲜。必称箕子者。所以示不臣周之意。非也。盖武王释囚之后。未及封建而即就问之也。
乃言二字。先儒之说虽多。而有可以两言句当者。武王初见箕子于商亡之后。必有慰释之言。而史皆略之。则一乃字。所以见先有慰释之言。然后乃为之言也。此一说也。九畴。是传道之大法。苟非圣人。不可得以闻。又非圣人。不可得以问。一乃字。所以示圣人然后乃可言之意也。此又一说也。
王乃言一节。先儒之论。多不合当。至于陈定于蔡九峰之以所以然释攸叙者。尤无意义。信如其言。则将如所答之非所问。何哉。况以武王之圣。必无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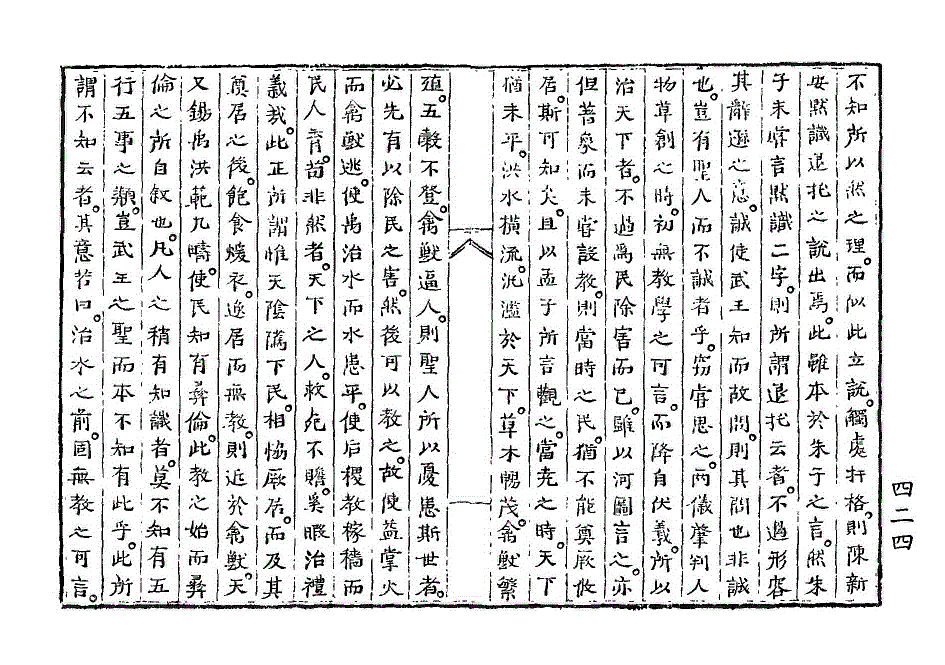 不知所以然之理。而似此立说。触处捍格。则陈新安默识退托之说出焉。此虽本于朱子之言。然朱子未尝言默识二字。则所谓退托云者。不过形容其辞逊之意。诚使武王知而故问。则其问也非诚也。岂有圣人而不诚者乎。窃尝思之。两仪肇判人物草创之时。初无教学之可言。而降自伏羲。所以治天下者。不过为民除害而已。虽以河图言之。亦但著象而未尝设教。则当时之民。犹不能奠厥攸居。斯可知矣。且以孟子所言观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汎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则圣人所以忧患斯世者。必先有以除民之害。然后可以教之。故使益掌火而禽兽逃。使禹治水而水患平。使后稷教稼穑而民人育。苟非然者。天下之人。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正所谓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而及其奠居之后。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天又锡禹洪范九畴。使民知有彝伦。此教之始而彝伦之所自叙也。凡人之稍有知识者。莫不知有五行五事之类。岂武王之圣而本不知有此乎。此所谓不知云者。其意若曰。治水之前。固无教之可言。
不知所以然之理。而似此立说。触处捍格。则陈新安默识退托之说出焉。此虽本于朱子之言。然朱子未尝言默识二字。则所谓退托云者。不过形容其辞逊之意。诚使武王知而故问。则其问也非诚也。岂有圣人而不诚者乎。窃尝思之。两仪肇判人物草创之时。初无教学之可言。而降自伏羲。所以治天下者。不过为民除害而已。虽以河图言之。亦但著象而未尝设教。则当时之民。犹不能奠厥攸居。斯可知矣。且以孟子所言观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汎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则圣人所以忧患斯世者。必先有以除民之害。然后可以教之。故使益掌火而禽兽逃。使禹治水而水患平。使后稷教稼穑而民人育。苟非然者。天下之人。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正所谓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而及其奠居之后。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天又锡禹洪范九畴。使民知有彝伦。此教之始而彝伦之所自叙也。凡人之稍有知识者。莫不知有五行五事之类。岂武王之圣而本不知有此乎。此所谓不知云者。其意若曰。治水之前。固无教之可言。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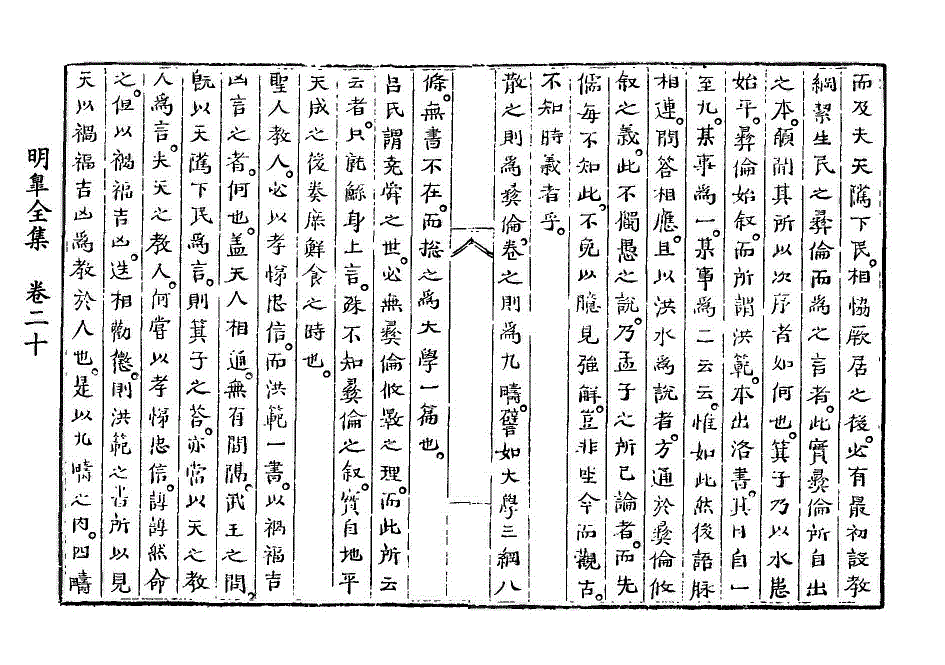 而及夫天骘下民。相协厥居之后。必有最初设教纲絜生民之彝伦而为之言者。此实彝伦所自出之本。愿闻其所以次序者如何也。箕子乃以水患始平。彝伦始叙。而所谓洪范。本出洛书。其目自一至九。某事为一。某事为二云云。惟如此然后语脉相连。问答相应。且以洪水为说者。方通于彝伦攸叙之义。此不独愚之说。乃孟子之所已论者。而先儒每不知此。不免以臆见强解。岂非坐今而观古。不知时义者乎。
而及夫天骘下民。相协厥居之后。必有最初设教纲絜生民之彝伦而为之言者。此实彝伦所自出之本。愿闻其所以次序者如何也。箕子乃以水患始平。彝伦始叙。而所谓洪范。本出洛书。其目自一至九。某事为一。某事为二云云。惟如此然后语脉相连。问答相应。且以洪水为说者。方通于彝伦攸叙之义。此不独愚之说。乃孟子之所已论者。而先儒每不知此。不免以臆见强解。岂非坐今而观古。不知时义者乎。散之则为彝伦。卷之则为九畴。譬如大学三纲八条。无书不在。而总之为大学一篇也。
吕氏谓尧舜之世。必无彝伦攸斁之理。而此所云云者。只就鲧身上言。殊不知彝伦之叙。实自地平天成之后奏庶鲜食之时也。
圣人教人。必以孝悌忠信。而洪范一书。以祸福吉凶言之者。何也。盖天人相通。无有间隔。武王之问。既以天骘下民为言。则箕子之答。亦当以天之教人为言。夫天之教人。何尝以孝悌忠信。谆谆然命之。但以祸福吉凶。迭相劝惩。则洪范之书所以见天以祸福吉凶为教于人也。是以九畴之内。四畴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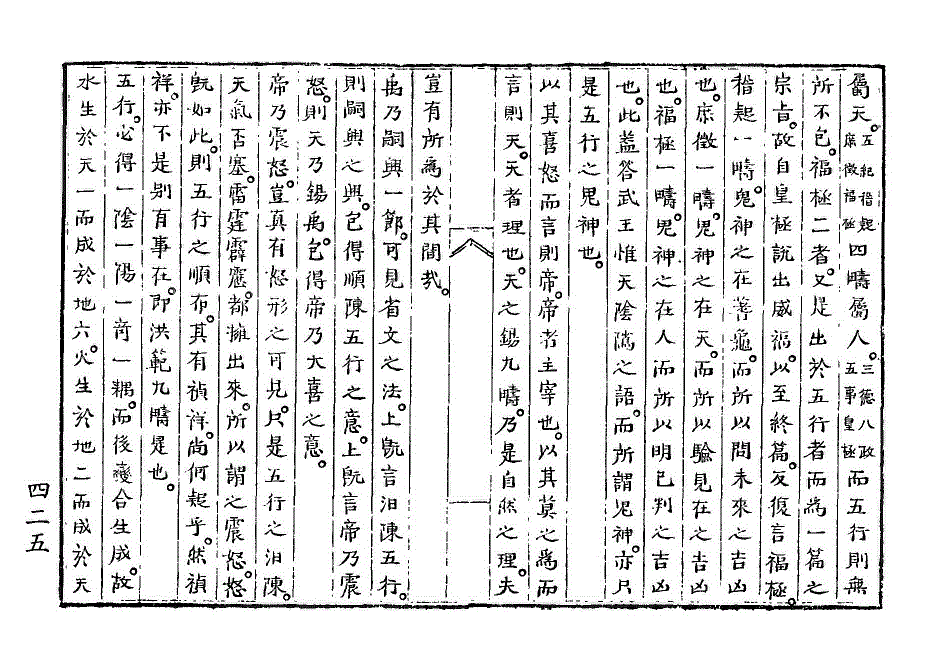 属天。(五纪稽疑庶徵福极)四畴属人。(三德八政五事皇极)而五行则无所不包。福极二者。又是出于五行者而为一篇之宗旨。故自皇极说出威福。以至终篇。反复言福极。稽疑一畴。鬼神之在蓍龟。而所以问未来之吉凶也。庶徵一畴。鬼神之在天。而所以验见在之吉凶也。福极一畴。鬼神之在人而所以明已判之吉凶也。此盖答武王惟天阴骘之语。而所谓鬼神。亦只是五行之鬼神也。
属天。(五纪稽疑庶徵福极)四畴属人。(三德八政五事皇极)而五行则无所不包。福极二者。又是出于五行者而为一篇之宗旨。故自皇极说出威福。以至终篇。反复言福极。稽疑一畴。鬼神之在蓍龟。而所以问未来之吉凶也。庶徵一畴。鬼神之在天。而所以验见在之吉凶也。福极一畴。鬼神之在人而所以明已判之吉凶也。此盖答武王惟天阴骘之语。而所谓鬼神。亦只是五行之鬼神也。以其喜怒而言则帝。帝者主宰也。以其莫之为而言则天。天者理也。天之锡九畴。乃是自然之理。夫岂有所为于其间哉。
禹乃嗣兴一节。可见省文之法。上既言汩陈五行。则嗣兴之兴。包得顺陈五行之意。上既言帝乃震怒。则天乃锡禹。包得帝乃大喜之意。
帝乃震怒。岂真有怒形之可见。只是五行之汩陈。天气否塞。雷霆霹雳。都拥出来。所以谓之震怒。怒既如此。则五行之顺布。其有祯祥。尚何疑乎。然祯祥。亦不是别有事在。即洪范九畴是也。
五行。必得一阴一阳一奇一耦。而后变合生成。故水生于天一而成于地六。火生于地二而成于天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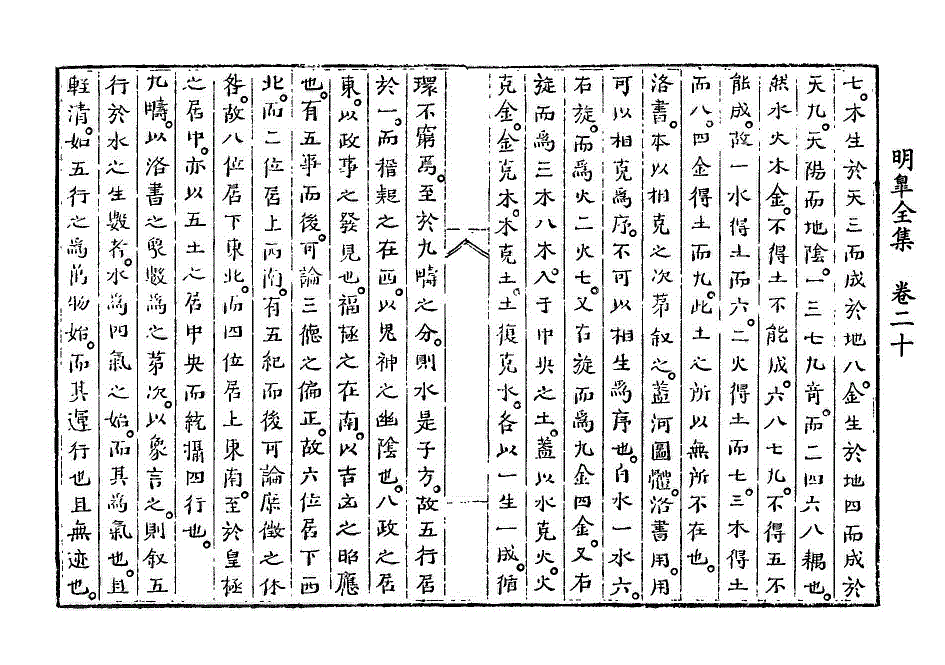 七。木生于天三而成于地八。金生于地四而成于天九。天阳而地阴。一三七九奇。而二四六八耦也。然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成。六八七九。不得五不能成。故一水得土而六。二火得土而七。三木得土而八。四金得土而九。此土之所以无所不在也。
七。木生于天三而成于地八。金生于地四而成于天九。天阳而地阴。一三七九奇。而二四六八耦也。然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成。六八七九。不得五不能成。故一水得土而六。二火得土而七。三木得土而八。四金得土而九。此土之所以无所不在也。洛书。本以相克之次第叙之。盖河图体。洛书用。用可以相克为序。不可以相生为序也。自水一水六。右旋。而为火二火七。又右旋而为九金四金。又右旋而为三木八木。入于中央之土。盖以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复克水。各以一生一成。循环不穷焉。至于九畴之分。则水是子方。故五行居于一。而稽疑之在西。以鬼神之幽阴也。八政之居东。以政事之发见也。福极之在南。以吉凶之昭应也。有五事而后。可论三德之偏正。故六位居下西北。而二位居上西南。有五纪而后可论庶徵之休咎。故八位居下东北。而四位居上东南。至于皇极之居中。亦以五土之居中央而统摄四行也。
九畴。以洛书之象数为之第次。以象言之。则叙五行于水之生数者。水为四气之始。而其为气也。且轻清。如五行之为万物始。而其运行也且无迹也。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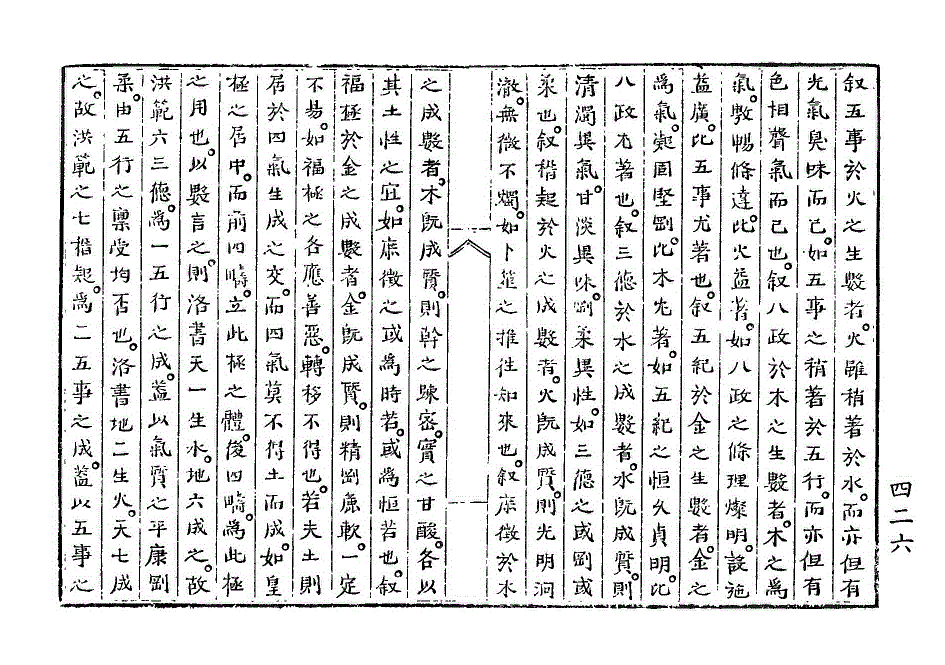 叙五事于火之生数者。火虽稍著于水。而亦但有光气臭味而已。如五事之稍著于五行。而亦但有色相声气而已也。叙八政于木之生数者。木之为气。敷畅条达。比火益著。如八政之条理灿明。设施益广。比五事尤著也。叙五纪于金之生数者。金之为气。凝固坚刚。比木尤著。如五纪之恒久贞明。比八政尤著也。叙三德于水之成数者。水既成质。则清浊异气。甘淡异味。刚柔异性。如三德之或刚或柔也。叙稽疑于火之成数者。火既成质。则光明泂澈。无微不烛。如卜筮之推往知来也。叙庶徵于木之成数者。木既成质。则干之疏密。实之甘酸。各以其土性之宜。如庶徵之或为时若。或为恒若也。叙福极于金之成数者。金既成质。则精刚粗软。一定不易。如福极之各应善恶。转移不得也。若夫土则居于四气生成之交。而四气莫不得土而成。如皇极之居中。而前四畴。立此极之体。后四畴。为此极之用也。以数言之。则洛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洪范六三德。为一五行之成。盖以气质之平康刚柔。由五行之禀受均否也。洛书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洪范之七稽疑。为二五事之成。盖以五事之
叙五事于火之生数者。火虽稍著于水。而亦但有光气臭味而已。如五事之稍著于五行。而亦但有色相声气而已也。叙八政于木之生数者。木之为气。敷畅条达。比火益著。如八政之条理灿明。设施益广。比五事尤著也。叙五纪于金之生数者。金之为气。凝固坚刚。比木尤著。如五纪之恒久贞明。比八政尤著也。叙三德于水之成数者。水既成质。则清浊异气。甘淡异味。刚柔异性。如三德之或刚或柔也。叙稽疑于火之成数者。火既成质。则光明泂澈。无微不烛。如卜筮之推往知来也。叙庶徵于木之成数者。木既成质。则干之疏密。实之甘酸。各以其土性之宜。如庶徵之或为时若。或为恒若也。叙福极于金之成数者。金既成质。则精刚粗软。一定不易。如福极之各应善恶。转移不得也。若夫土则居于四气生成之交。而四气莫不得土而成。如皇极之居中。而前四畴。立此极之体。后四畴。为此极之用也。以数言之。则洛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洪范六三德。为一五行之成。盖以气质之平康刚柔。由五行之禀受均否也。洛书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洪范之七稽疑。为二五事之成。盖以五事之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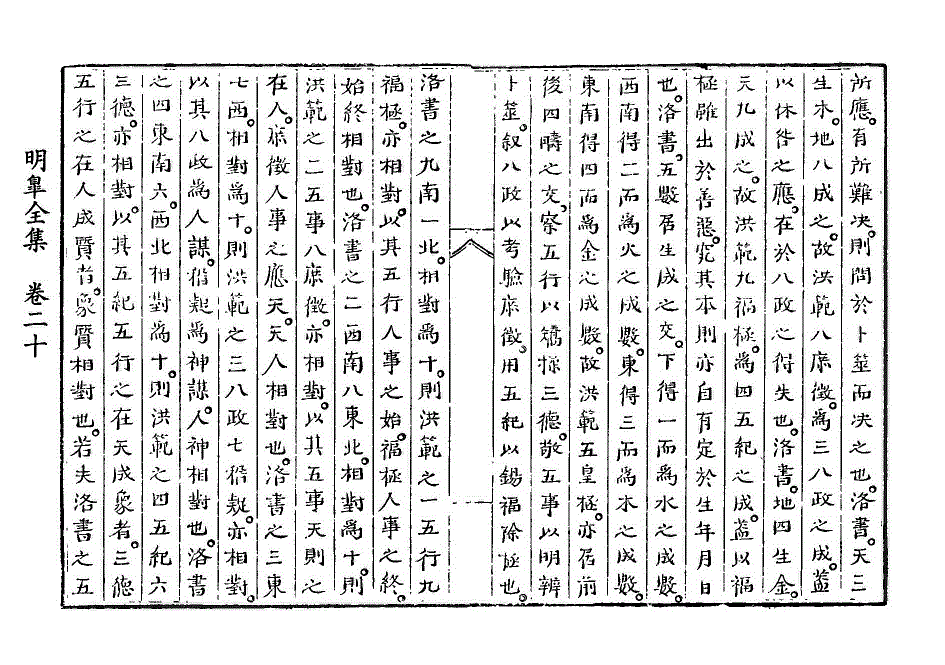 所应。有所难决。则问于卜筮而决之也。洛书。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洪范八庶徵。为三八政之成。盖以休咎之应。在于八政之得失也。洛书。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洪范九福极。为四五纪之成。盖以福极虽出于善恶。究其本则亦自有定于生年月日也。洛书。五数居生成之交。下得一而为水之成数。西南得二而为火之成数。东得三而为木之成数。东南得四而为金之成数。故洪范五皇极。亦居前后四畴之交。察五行以矫揉三德。敬五事以明辨卜筮。叙八政以考验庶徵。用五纪以锡福除极也。洛书之九南一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一五行九福极。亦相对。以其五行人事之始。福极人事之终。始终相对也。洛书之二西南八东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二五事八庶徵。亦相对。以其五事天则之在人。庶徵人事之应天。天人相对也。洛书之三东七西。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三八政七稽疑。亦相对。以其八政为人谋。稽疑为神谋。人神相对也。洛书之四东南六。西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四五纪六三德。亦相对。以其五纪五行之在天成象者。三德五行之在人成质者。象质相对也。若夫洛书之五
所应。有所难决。则问于卜筮而决之也。洛书。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洪范八庶徵。为三八政之成。盖以休咎之应。在于八政之得失也。洛书。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洪范九福极。为四五纪之成。盖以福极虽出于善恶。究其本则亦自有定于生年月日也。洛书。五数居生成之交。下得一而为水之成数。西南得二而为火之成数。东得三而为木之成数。东南得四而为金之成数。故洪范五皇极。亦居前后四畴之交。察五行以矫揉三德。敬五事以明辨卜筮。叙八政以考验庶徵。用五纪以锡福除极也。洛书之九南一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一五行九福极。亦相对。以其五行人事之始。福极人事之终。始终相对也。洛书之二西南八东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二五事八庶徵。亦相对。以其五事天则之在人。庶徵人事之应天。天人相对也。洛书之三东七西。相对为十。则洪范之三八政七稽疑。亦相对。以其八政为人谋。稽疑为神谋。人神相对也。洛书之四东南六。西北相对为十。则洪范之四五纪六三德。亦相对。以其五纪五行之在天成象者。三德五行之在人成质者。象质相对也。若夫洛书之五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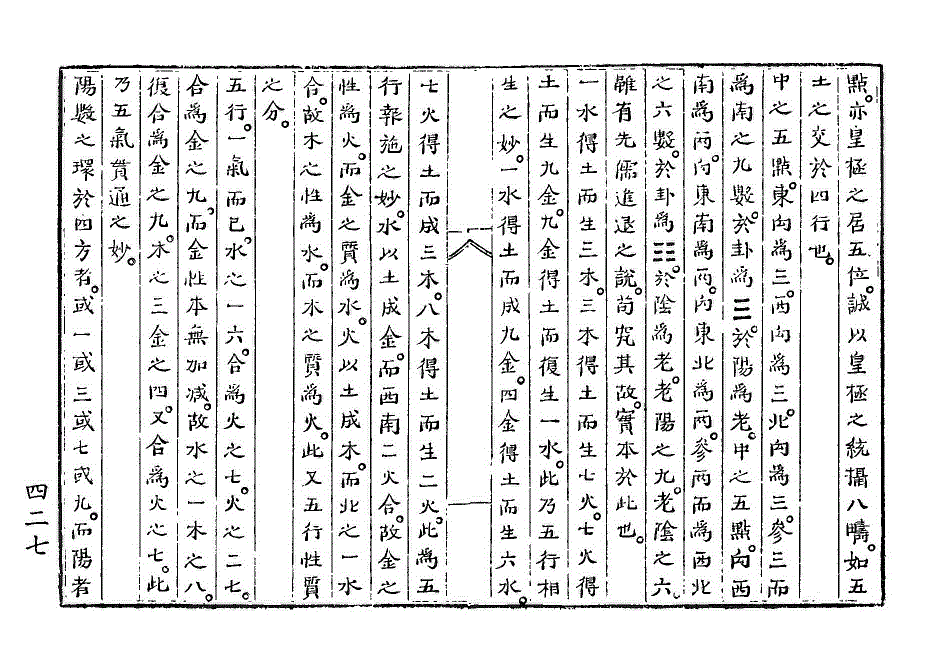 点。亦皇极之居五位。诚以皇极之统摄八畴。如五土之交于四行也。
点。亦皇极之居五位。诚以皇极之统摄八畴。如五土之交于四行也。中之五点。东向为三。西向为三。北向为三。参三而为南之九数。于卦为☰。于阳为老。中之五点。向西南为两。向东南为两。向东北为两。参两而为西北之六数。于卦为☷。于阴为老。老阳之九。老阴之六。虽有先儒进退之说。苟究其故。实本于此也。
一水得土而生三木。三木得土而生七火。七火得土而生九金。九金得土而复生一水。此乃五行相生之妙。一水得土而成九金。四金得土而生六水。七火得土而成三木。八木得土而生二火。此为五行报施之妙。水以土成金。而西南二火合。故金之性为火。而金之质为水。火以土成木。而北之一水合。故木之性为水。而木之质为火。此又五行性质之分。
五行。一气而已。水之一六。合为火之七。火之二七。合为金之九。而金性本无加减。故水之一木之八。复合为金之九。木之三金之四。又合为火之七。此乃五气贯通之妙。
阳数之环于四方者。或一或三或七或九。而阳者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8H 页
 圆也。以径一围三率之。则一亦三也。三亦三也。七亦三也。此则以中五之径数计之。而所以为参三为九之妙也。阴数之环于四方者。或二或四或六或八。而阴者方也。以径一围四率之。则二亦二也。四亦二也。八亦二也。此则以中五之围数计之。而所以为参两为六之妙也。
圆也。以径一围三率之。则一亦三也。三亦三也。七亦三也。此则以中五之径数计之。而所以为参三为九之妙也。阴数之环于四方者。或二或四或六或八。而阴者方也。以径一围四率之。则二亦二也。四亦二也。八亦二也。此则以中五之围数计之。而所以为参两为六之妙也。参三而为天数之九。参两而为地数之六。合为十五。洛书之纵横十五。观于此。可知其所以然。
奇数之一三五。合而为九。此老阳所以为九也。偶数之二四合而为六。此老阴所以为六也。
生数奇三而偶二。故成数偶三而奇二。此又生成交错之妙。
水火木金土。天地未成形之前五气。以此次序。成天地之形。木火土金水。天地已成形之后五气。以此次序。行天地之用。盖水火木金土。乃气化之五行。木火土金水。乃形化之五行。
九畴。自一至九。各言体用。以五行言之。水火木金土。体之五也。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用之行也。言五而不言行。无以知五者之用。言行而不言五。无以知本体之数。五行二字。不可少一也。以五事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8L 页
 言之。貌言视听思。体之五也。恭聪从明睿。用之事也。言五而不言事。无以知五者之用。言事而不言五。无以知本体之数。五事二字。不可少一也。以八政言之。上四者体也。下四者用也。先言八以见体用之全数。后言政以见天叙其体而人得其用也。言八而不言政。无以知八者之为用。言政而不言八。无以知体用之为几。八政二字。不可少一也。以五纪言之。岁日月星辰。体之数也。历数。用以纪也。言五而不言纪。无以知天道之为用。言纪而不言数。无以知天象之为几。五纪二字。不可少一也。以皇极言之。皇建其有极。体也。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用也。言极而不言皇。无以知敛敷者为谁。言皇而不言极。无以知其体之为至也。皇极二字。不可少一也。以三德言之。正直刚克柔克。体之三也。弗友沉潜之刚克。燮友高明之柔克。用之德也。言三而不言德。无以知人君之克民。言德而不言三。无以知所克者为几。三德二字。不可少一也。以稽疑言之。凡七者。体也。卜五占用二者。用也。以庶徵言之。雨旸燠寒风。体之庶也。曰时者。徵之用也。以福极言之。在天曰寿曰富曰康宁曰凶短折曰疾
言之。貌言视听思。体之五也。恭聪从明睿。用之事也。言五而不言事。无以知五者之用。言事而不言五。无以知本体之数。五事二字。不可少一也。以八政言之。上四者体也。下四者用也。先言八以见体用之全数。后言政以见天叙其体而人得其用也。言八而不言政。无以知八者之为用。言政而不言八。无以知体用之为几。八政二字。不可少一也。以五纪言之。岁日月星辰。体之数也。历数。用以纪也。言五而不言纪。无以知天道之为用。言纪而不言数。无以知天象之为几。五纪二字。不可少一也。以皇极言之。皇建其有极。体也。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用也。言极而不言皇。无以知敛敷者为谁。言皇而不言极。无以知其体之为至也。皇极二字。不可少一也。以三德言之。正直刚克柔克。体之三也。弗友沉潜之刚克。燮友高明之柔克。用之德也。言三而不言德。无以知人君之克民。言德而不言三。无以知所克者为几。三德二字。不可少一也。以稽疑言之。凡七者。体也。卜五占用二者。用也。以庶徵言之。雨旸燠寒风。体之庶也。曰时者。徵之用也。以福极言之。在天曰寿曰富曰康宁曰凶短折曰疾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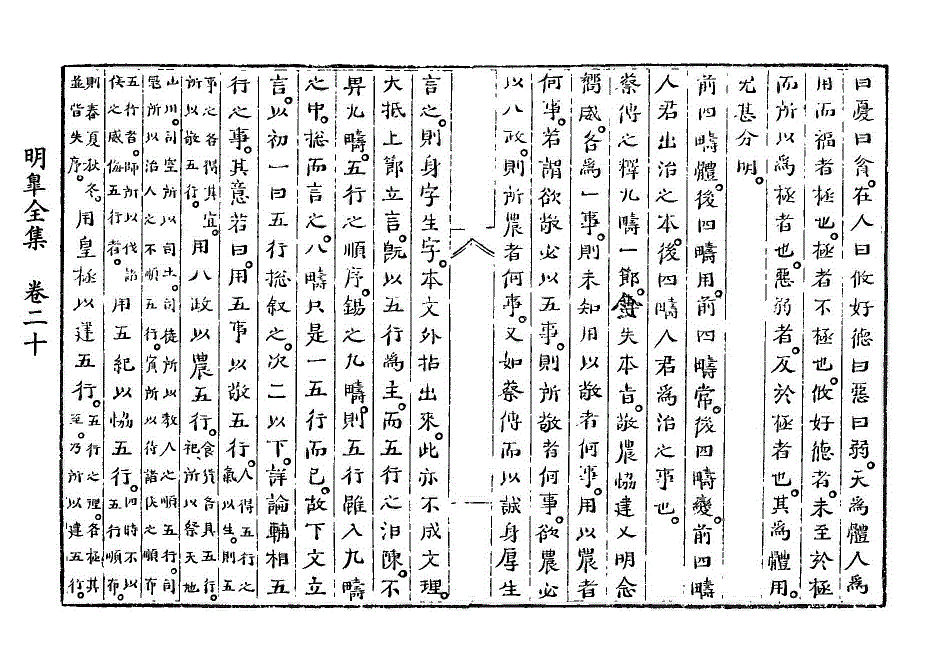 曰忧曰贫。在人曰攸好德曰恶曰弱。天为体人为用而福者极也。极者不极也。攸好德者。未至于极而所以为极者也。恶弱者。反于极者也。其为体用。尤甚分明。
曰忧曰贫。在人曰攸好德曰恶曰弱。天为体人为用而福者极也。极者不极也。攸好德者。未至于极而所以为极者也。恶弱者。反于极者也。其为体用。尤甚分明。前四畴体。后四畴用。前四畴常。后四畴变。前四畴人君出治之本。后四畴人君为治之事也。
蔡传之释九畴一节。全失本旨。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各为一事。则未知用以敬者何事。用以农者何事。若谓欲敬必以五事。则所敬者何事。欲农必以八政。则所农者何事。又如蔡传而以诚身厚生言之。则身字生字。本文外拈出来。此亦不成文理。大抵上节立言。既以五行为主。而五行之汩陈。不畀九畴。五行之顺序。锡之九畴。则五行虽入九畴之中。总而言之。八畴只是一五行而已。故下文立言。以初一曰五行总叙之。次二以下。详论辅相五行之事。其意若曰。用五事以敬五行。(人得五行之气以生。则五事之各得其宜。所以敬五行。)用八政以农五行。(食货各具五行。祀所以祭天地山川。司空所以司土。司徒所以教人之顺五行。司寇所以治人之不顺五行。宾所以待诸侯之顺布五行者。师所以伐诸侯之威侮五行者。)用五纪以协五行。(四时不以五行顺布。则春夏秋冬。并皆失序。)用皇极以建五行。(五行之理。各极其至。乃所以建五行。)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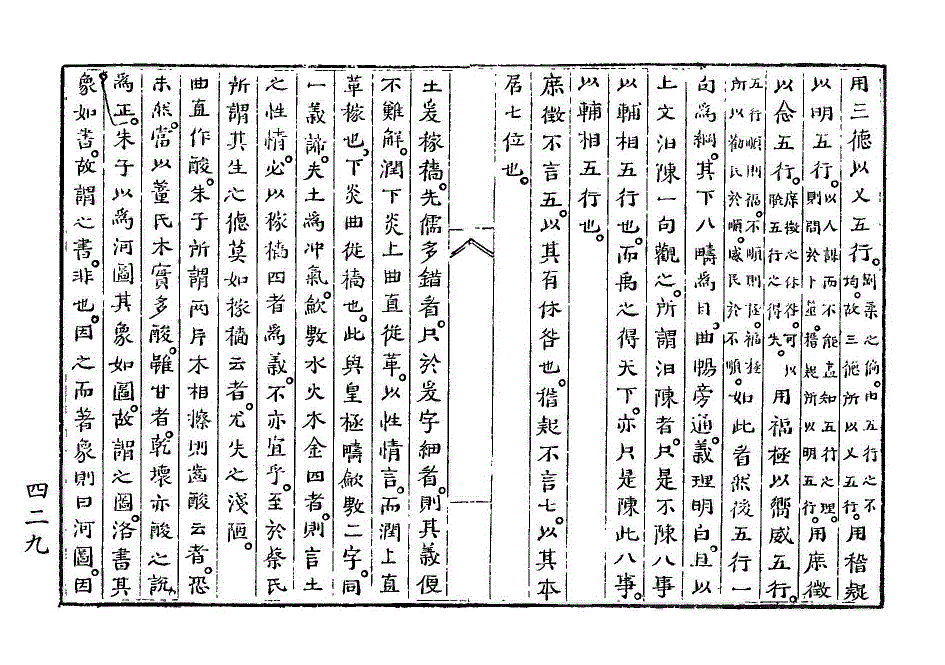 用三德以乂五行。(刚柔之偏。由五行之不均。故三德所以乂五行。)用稽疑以明五行。(以人谋而不能尽知五行之理。则问于卜筮。稽疑所以明五行。)用庶徵以念五行。(庶徵之休咎。可以验五行之得失。)用福极以向威五行。(五行顺则福。不顺则极。福极所以劝民于顺。威民于不顺。)如此看然后五行一句为纲。其下八畴为目。曲畅旁通。义理明白。且以上文汩陈一句观之。所谓汩陈者。只是不陈八事以辅相五行也。而禹之得天下。亦只是陈此八事。以辅相五行也。
用三德以乂五行。(刚柔之偏。由五行之不均。故三德所以乂五行。)用稽疑以明五行。(以人谋而不能尽知五行之理。则问于卜筮。稽疑所以明五行。)用庶徵以念五行。(庶徵之休咎。可以验五行之得失。)用福极以向威五行。(五行顺则福。不顺则极。福极所以劝民于顺。威民于不顺。)如此看然后五行一句为纲。其下八畴为目。曲畅旁通。义理明白。且以上文汩陈一句观之。所谓汩陈者。只是不陈八事以辅相五行也。而禹之得天下。亦只是陈此八事。以辅相五行也。庶徵不言五。以其有休咎也。稽疑不言七。以其本居七位也。
土爰稼穑。先儒多错看。只于爰字细看。则其义便不难解。润下炎上曲直从革。以性情言。而润上直革稼也。下炎曲从穑也。此与皇极畴敛敷二字。同一义谛。夫土为冲气。敛敷水火木金四者。则言土之性情。必以稼穑四者为义。不亦宜乎。至于蔡氏所谓其生之德莫如稼穑云者。尤失之浅陋。
曲直作酸。朱子所谓两片木相擦则齿酸云者。恐未然。当以蕫氏木实多酸。虽甘者。乾坏亦酸之说。为正。朱子以为河图其象如图。故谓之图。洛书其象如书。故谓之书。非也。因之而著象则曰河图。因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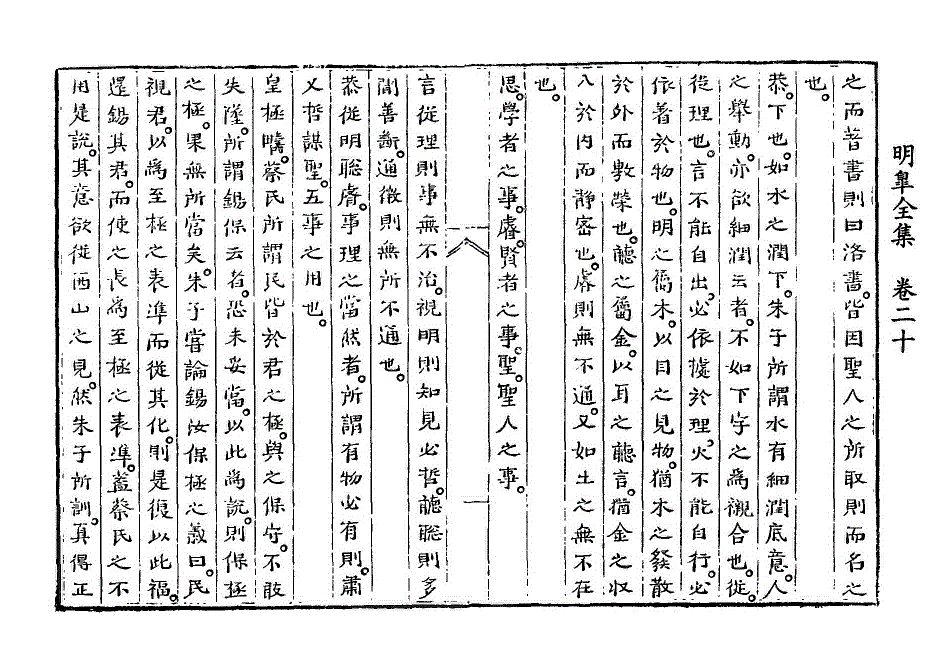 之而著书则曰洛书。皆因圣人之所取则而名之也。
之而著书则曰洛书。皆因圣人之所取则而名之也。恭。下也。如水之润下。朱子所谓水有细润底意。人之举动。亦欲细润云者。不如下字之为衬合也。从。从理也。言不能自出。必依据于理。火不能自行。必依着于物也。明之属木。以目之见物。犹木之发散于外而敷荣也。听之属金。以耳之听言。犹金之收入于内而静密也。睿则无不通。又如土之无不在也。
思。学者之事。睿。贤者之事。圣。圣人之事。
言从理则事无不治。视明则知见必哲。听聪则多闻善断。通微则无所不通也。
恭从明聪睿。事理之当然者。所谓有物必有则。肃乂哲谋圣。五事之用也。
皇极畴。蔡氏所谓民皆于君之极。与之保守。不敢失坠。所谓锡保云者。恐未妥当。以此为说。则保极之极。果无所当矣。朱子尝论锡汝保极之义曰。民视君。以为至极之表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表准。盖蔡氏之不用是说。其意欲从西山之见。然朱子所训。真得正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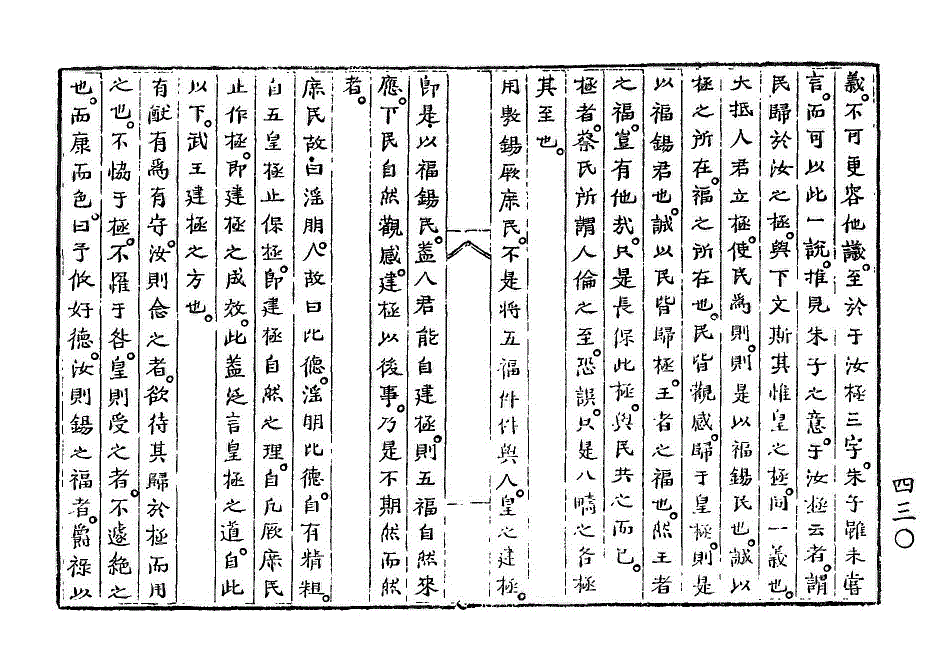 义。不可更容他议。至于于汝极三字。朱子虽未尝言。而可以此一说。推见朱子之意。于汝极云者。谓民归于汝之极。与下文斯其惟皇之极。同一义也。大抵人君立极。使民为则。则是以福锡民也。诚以极之所在。福之所在也。民皆观感。归于皇极。则是以福锡君也。诚以民皆归极。王者之福也。然王者之福。岂有他哉。只是长保此极。与民共之而已。
义。不可更容他议。至于于汝极三字。朱子虽未尝言。而可以此一说。推见朱子之意。于汝极云者。谓民归于汝之极。与下文斯其惟皇之极。同一义也。大抵人君立极。使民为则。则是以福锡民也。诚以极之所在。福之所在也。民皆观感。归于皇极。则是以福锡君也。诚以民皆归极。王者之福也。然王者之福。岂有他哉。只是长保此极。与民共之而已。极者。蔡氏所谓人伦之至。恐误。只是八畴之各极其至也。
用敷锡厥庶民。不是将五福件件与人。皇之建极。即是以福锡民。盖人君能自建极。则五福自然来应。下民自然观感。建极以后事。乃是不期然而然者。
庶民故曰淫朋。人故曰比德。淫朋比德。自有精粗。自五皇极止保极。即建极自然之理。自凡厥庶民止作极。即建极之成效。此盖泛言皇极之道。自此以下。武王建极之方也。
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者。欲待其归于极而用之也。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者。不遽绝之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者。爵禄以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1H 页
 锡之也。此以三等言。(而康而色。上等也。有猷有为。中等也。不协于极。不罹于咎。下等也。)而末又结之曰。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则虽上等之人。亦言其资质然耳。非谓已至此极也。
锡之也。此以三等言。(而康而色。上等也。有猷有为。中等也。不协于极。不罹于咎。下等也。)而末又结之曰。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则虽上等之人。亦言其资质然耳。非谓已至此极也。有猷有为一节。与五事相表里。有猷者谋也。有为者哲也。有守者思也。此就五事之中。各能一事之人也。而康而色者。恭也。曰者。从也。攸好德者。聪明睿也。此兼能五事之人也。故人君所以用之者。亦有差等。于其能五事之人则锡之福。于其能一事之人则念之而已。此其义。皎如指掌。而虽朱子之说。亦未曾及此。乃曰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为名。则虽未必尽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名而与之善。盖缘曰字之泛看而有此解也。若然则建极之君。进用盗名之人。而所谓锡福之臣。只以色康而得之耶。恐未必然也。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此乃统天下说。言皇能如此则天下之人无不惟皇之极也。陈氏所谓时人指三等之人者。恐未是。
前既以庶民分三等言。无虐煢独一句。又承上接下。而此又以为有位而有才智者。当使之进而行其道。夫虽正人。必忠信重禄。然后可以有好心于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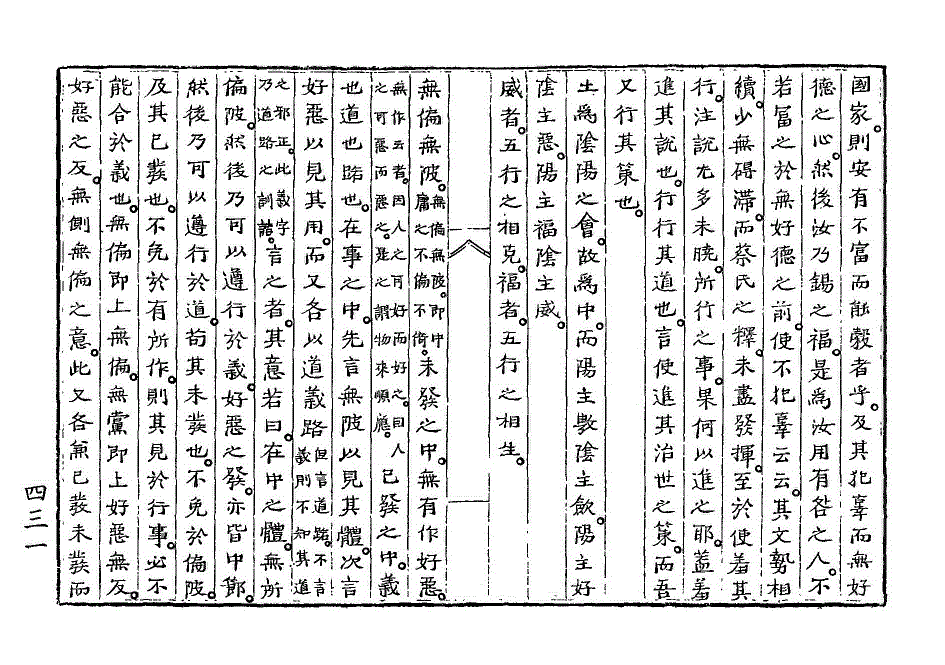 国家。则安有不富而能谷者乎。及其犯辜而无好德之心。然后汝乃锡之福。是为汝用有咎之人。不若富之于无好德之前。使不犯辜云云。其文势相续。少无碍滞。而蔡氏之释。未尽发挥。至于使羞其行。注说尤多未晓。所行之事。果何以进之耶。盖羞进其说也。行行其道也。言使进其治世之策。而吾又行其策也。
国家。则安有不富而能谷者乎。及其犯辜而无好德之心。然后汝乃锡之福。是为汝用有咎之人。不若富之于无好德之前。使不犯辜云云。其文势相续。少无碍滞。而蔡氏之释。未尽发挥。至于使羞其行。注说尤多未晓。所行之事。果何以进之耶。盖羞进其说也。行行其道也。言使进其治世之策。而吾又行其策也。土为阴阳之会。故为中。而阳主敷阴主敛。阳主好阴主恶。阳主福阴主威。
威者。五行之相克。福者。五行之相生。
无偏无陂。(无偏无陂。即中庸之不偏不倚。)未发之中。无有作好恶。(无作云者。因人之可好而好之。因人之可恶而恶之。是之谓物来顺应。)已发之中。义也道也路也。在事之中。先言无陂以见其体。次言好恶以见其用。而又各以道义路(但言道路。不言义则不知其道之邪正。此义字乃道路之训诰。)言之者。其意若曰。在中之体。无所偏陂。然后乃可以遵行于义。好恶之发。亦皆中节。然后乃可以遵行于道。苟其未发也。不免于偏陂。及其已发也。不免于有所作。则其见于行事。必不能合于义也。无偏即上无偏。无党即上好恶。无反好恶之反。无侧无偏之意。此又各兼已发未发而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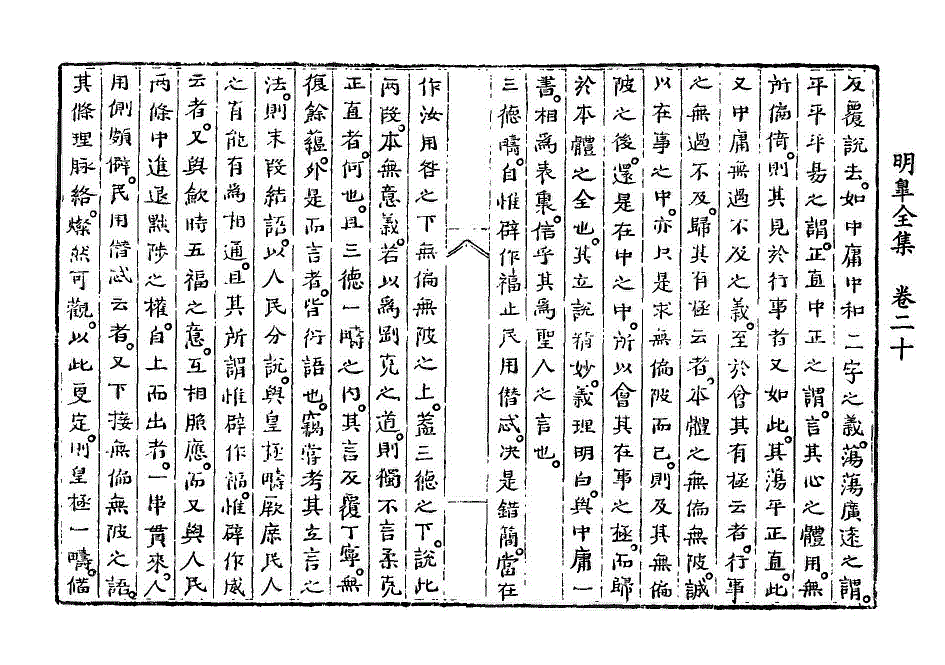 反覆说去。如中庸中和二字之义。荡荡广远之谓。平平平易之谓。正直中正之谓。言其心之体用。无所偏倚。则其见于行事者又如此。其荡平正直。此又中庸无过不及之义。至于会其有极云者。行事之无过不及。归其有极云者。本体之无偏无陂。诚以在事之中。亦只是求无偏陂而已。则及其无偏陂之后。还是在中之中。所以会其在事之极。而归于本体之全也。其立说精妙。义理明白。与中庸一书。相为表里。信乎其为圣人之言也。
反覆说去。如中庸中和二字之义。荡荡广远之谓。平平平易之谓。正直中正之谓。言其心之体用。无所偏倚。则其见于行事者又如此。其荡平正直。此又中庸无过不及之义。至于会其有极云者。行事之无过不及。归其有极云者。本体之无偏无陂。诚以在事之中。亦只是求无偏陂而已。则及其无偏陂之后。还是在中之中。所以会其在事之极。而归于本体之全也。其立说精妙。义理明白。与中庸一书。相为表里。信乎其为圣人之言也。三德畴。自惟辟作福止民用僭忒。决是错简。当在作汝用咎之下无偏无陂之上。盖三德之下。说此两段。本无意义。若以为刚克之道。则独不言柔克正直者。何也。且三德一畴之内。其言反覆丁宁。无复馀蕴。外是而言者。皆衍语也。窃尝考其立言之法。则末段结语。以人民分说。与皇极畴厥庶民人之有能有为相通。且其所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云者。又与敛时五福之意。互相照应。而又与人民两条中进退黜陟之权。自上而出者。一串贯来。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云者。又下接无偏无陂之语。其条理脉络。灿然可观。以此更定。则皇极一畴。备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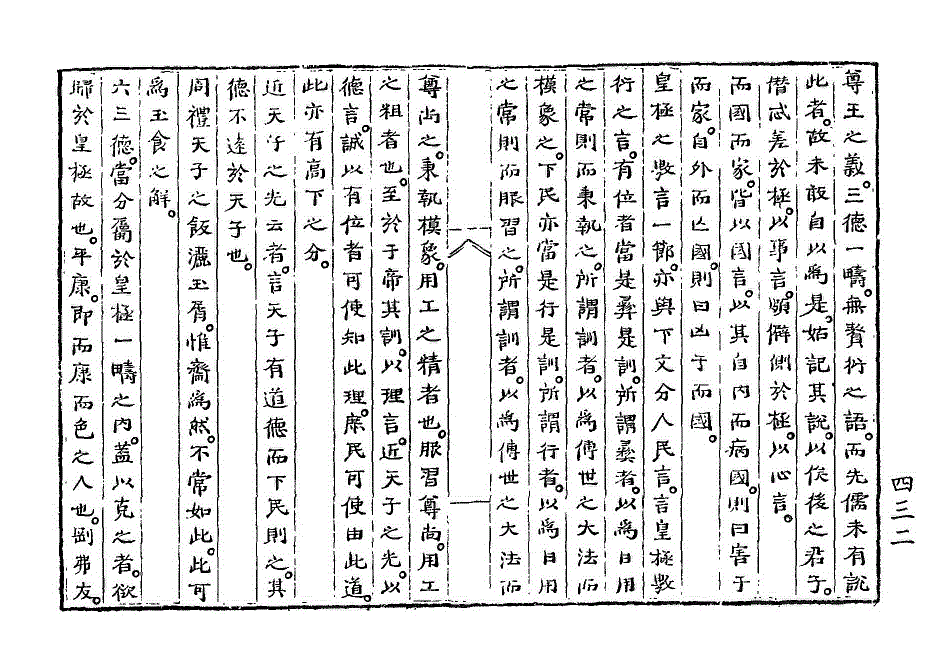 尊王之义。三德一畴。无赘衍之语。而先儒未有说此者。故未敢自以为是。姑记其说。以俟后之君子。僭忒差于极。以事言。颇僻侧于极。以心言。
尊王之义。三德一畴。无赘衍之语。而先儒未有说此者。故未敢自以为是。姑记其说。以俟后之君子。僭忒差于极。以事言。颇僻侧于极。以心言。而国而家。皆以国言。以其自内而病国。则曰害于而家。自外而亡国。则曰凶于而国。
皇极之敷言一节。亦与下文分人民言。言皇极敷衍之言。有位者当是彝是训。所谓彝者。以为日用之常则而秉执之。所谓训者。以为传世之大法而模象之。下民亦当是行是训。所谓行者。以为日用之常则而服习之。所谓训者。以为传世之大法而尊尚之。秉执模象。用工之精者也。服习尊尚。用工之粗者也。至于于帝其训。以理言。近天子之光。以德言。诚以有位者可使知此理。庶民可使由此道。此亦有高下之分。
近天子之光云者。言天子有道德而下民则之其德。不远于天子也。
周礼天子之饭洒玉屑。惟斋为然。不常如此。此可为玉食之解。
六三德。当分属于皇极一畴之内。盖以克之者。欲归于皇极故也。平康。即而康而色之人也。刚弗友。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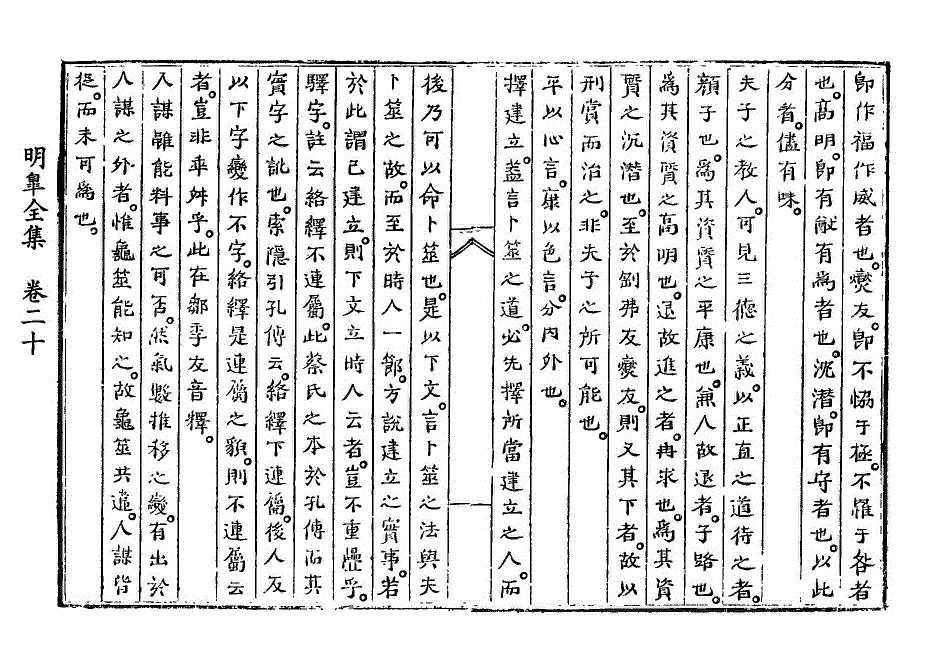 即作福作威者也。燮友。即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也。高明。即有猷有为者也。沈潜。即有守者也。以此分看。尽有味。
即作福作威者也。燮友。即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也。高明。即有猷有为者也。沈潜。即有守者也。以此分看。尽有味。夫子之教人。可见三德之义。以正直之道待之者。颜子也。为其资质之平康也。兼人故退者。子路也。为其资质之高明也。退故进之者。冉求也。为其资质之沉潜也。至于刚弗友燮友。则又其下者。故以刑赏而治之。非夫子之所可能也。
平以心言。康以色言。分内外也。
择建立。盖言卜筮之道。必先择所当建立之人。而后乃可以命卜筮也。是以下文。言卜筮之法与夫卜筮之故。而至于时人一节。方说建立之实事。若于此谓已建立。则下文立时人云者。岂不重叠乎。驿字。注云络绎不连属。此蔡氏之本于孔传而其实字之讹也。索隐引孔传云。络绎下连属。后人反以下字变作不字。络绎是连属之貌。则不连属云者。岂非乖舛乎。此在邹季友音释。
人谋虽能料事之可否。然气数推移之变。有出于人谋之外者。惟龟筮能知之。故龟筮共违。人谋皆从。而未可为也。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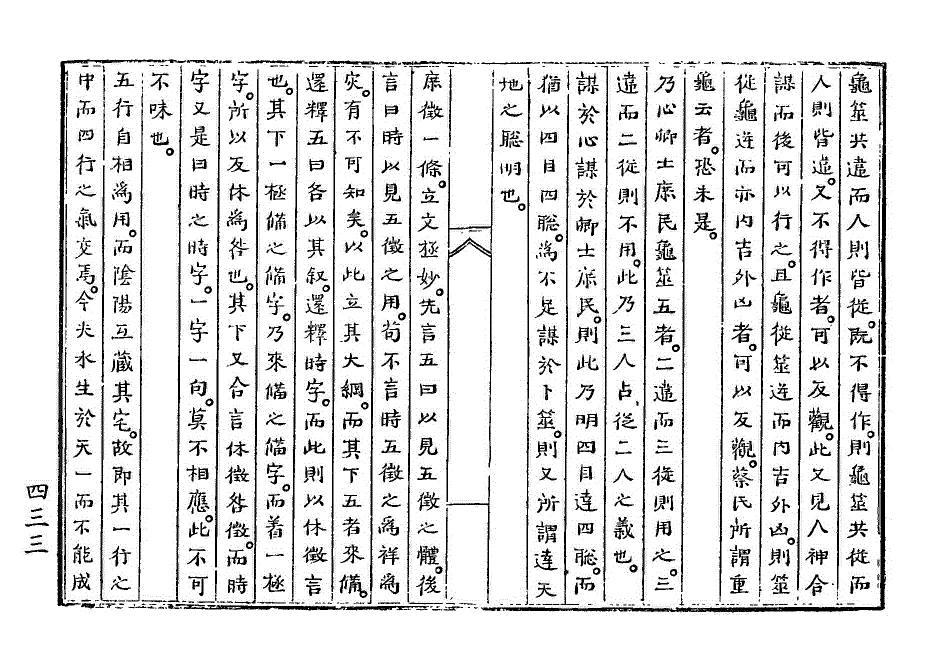 龟筮共违而人则皆从。既不得作。则龟筮共从而人则皆违。又不得作者。可以反观。此又见人神合谋而后可以行之。且龟从筮逆而内吉外凶。则筮从龟逆而亦内吉外凶者。可以反观。蔡氏所谓重龟云者。恐未是。
龟筮共违而人则皆从。既不得作。则龟筮共从而人则皆违。又不得作者。可以反观。此又见人神合谋而后可以行之。且龟从筮逆而内吉外凶。则筮从龟逆而亦内吉外凶者。可以反观。蔡氏所谓重龟云者。恐未是。乃心卿士庶民龟筮五者。二违而三从则用之。三违而二从则不用。此乃三人占从二人之义也。
谋于心谋于卿士庶民。则此乃明四目达四聪。而犹以四目四聪。为不足谋于卜筮。则又所谓达天地之聪明也。
庶徵一条。立文极妙。先言五曰以见五徵之体。后言曰时以见五徵之用。苟不言时五徵之为祥为灾。有不可知矣。以此立其大纲。而其下五者来备。还释五曰各以其叙。还释时字。而此则以休徵言也。其下一极备之备字。乃来备之备字。而着一极字。所以反休为咎也。其下又合言休徵咎徵。而时字又是曰时之时字。一字一句。莫不相应。此不可不味也。
五行自相为用。而阴阳互藏其宅。故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行之气交焉。今夫水生于天一而不能成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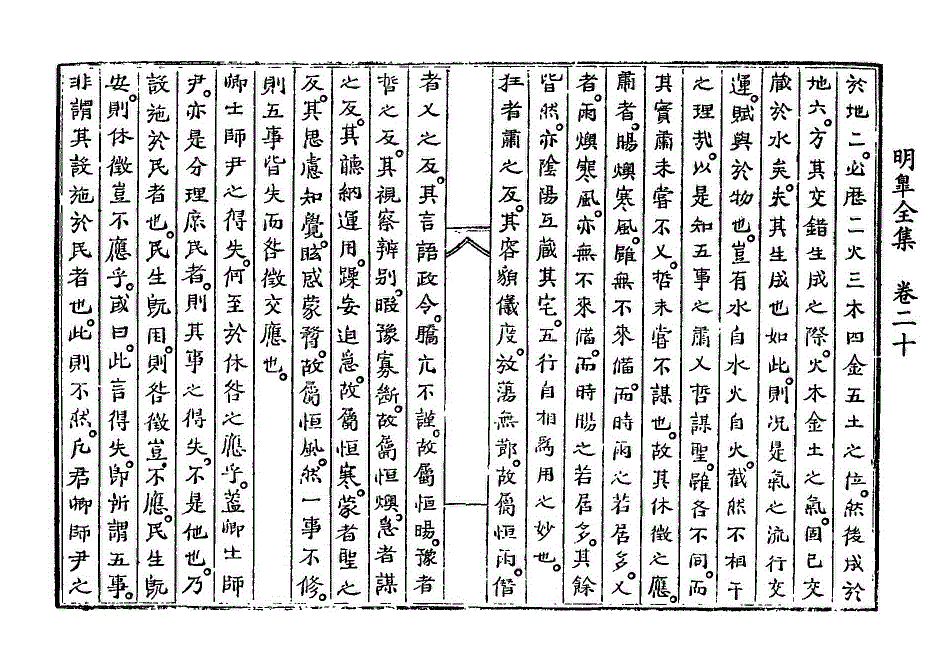 于地二。必历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之位。然后成于地六。方其交错生成之际。火木金土之气。固已交藏于水矣。夫其生成也如此。则况是气之流行交运。赋与于物也。岂有水自水火自火。截然不相干之理哉。以是知五事之肃乂哲谋圣。虽各不同。而其实肃未尝不乂。哲未尝不谋也。故其休徵之应。肃者。旸燠寒风。虽无不来备。而时雨之若居多。乂者。雨燠寒风。亦无不来备。而时旸之若居多。其馀皆然。亦阴阳互藏其宅。五行自相为用之妙也。
于地二。必历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之位。然后成于地六。方其交错生成之际。火木金土之气。固已交藏于水矣。夫其生成也如此。则况是气之流行交运。赋与于物也。岂有水自水火自火。截然不相干之理哉。以是知五事之肃乂哲谋圣。虽各不同。而其实肃未尝不乂。哲未尝不谋也。故其休徵之应。肃者。旸燠寒风。虽无不来备。而时雨之若居多。乂者。雨燠寒风。亦无不来备。而时旸之若居多。其馀皆然。亦阴阳互藏其宅。五行自相为用之妙也。狂者肃之反。其容貌仪度。放荡无节。故属恒雨。僭者乂之反。其言语政令。骄亢不谨。故属恒旸。豫者哲之反。其视察辨别。暇豫寡断。故属恒燠。急者谋之反。其听纳运用。躁妄迫急。故属恒寒。蒙者圣之反。其思虑知觉。眩惑蒙瞀。故属恒风。然一事不修。则五事皆失而咎徵交应也。
卿士师尹之得失。何至于休咎之应乎。盖卿士师尹。亦是分理庶民者。则其事之得失。不是他也。乃设施于民者也。民生既困。则咎徵岂不应。民生既安。则休徵岂不应乎。或曰。此言得失。即所谓五事。非谓其设施于民者也。此则不然。凡君卿师尹之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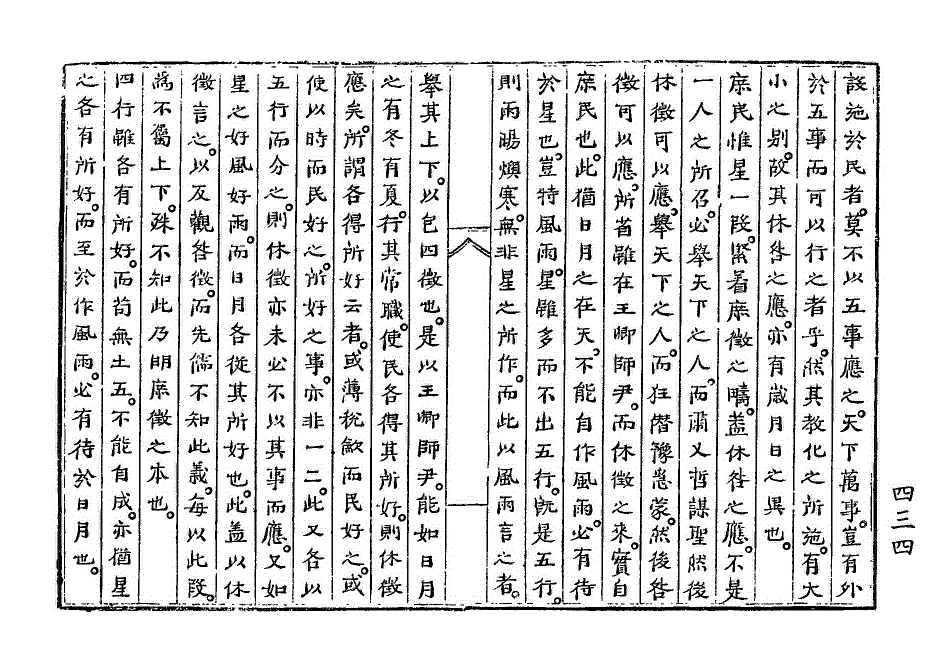 设施于民者。莫不以五事应之。天下万事。岂有外于五事而可以行之者乎。然其教化之所施。有大小之别。故其休咎之应。亦有岁月日之异也。
设施于民者。莫不以五事应之。天下万事。岂有外于五事而可以行之者乎。然其教化之所施。有大小之别。故其休咎之应。亦有岁月日之异也。庶民惟星一段。紧着庶徵之畴。盖休咎之应。不是一人之所召。必举天下之人。而肃乂哲谋圣然后休徵可以应。举天下之人。而狂僭豫急蒙。然后咎徵可以应。所省虽在王卿师尹。而休徵之来。实自庶民也。此犹日月之在天。不能自作风雨。必有待于星也。岂特风雨。星虽多而不出五行。既是五行。则雨旸燠寒。无非星之所作。而此以风雨言之者。举其上下。以包四徵也。是以王卿师尹。能如日月之有冬有夏。行其常职。使民各得其所好。则休徵应矣。所谓各得所好云者。或薄税敛而民好之。或使以时而民好之。所好之事。亦非一二。此又各以五行而分之。则休徵亦未必不以其事而应。又如星之好风好雨。而日月各从其所好也。此盖以休徵言之。以反观咎徵。而先儒不知此义。每以此段。为不属上下。殊不知此乃明庶徵之本也。
四行虽各有所好。而苟无土五。不能自成。亦犹星之各有所好。而至于作风雨。必有待于日月也。
明皋全集卷之二十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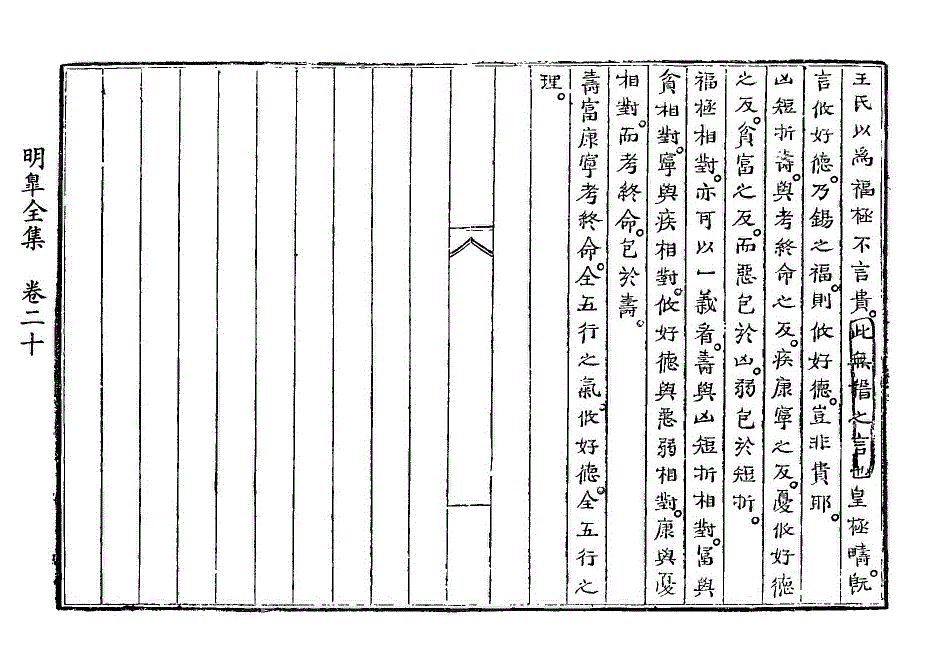 王氏以为福极不言贵。此无稽之言也。皇极畴。既言攸好德。乃锡之福。则攸好德。岂非贵耶。
王氏以为福极不言贵。此无稽之言也。皇极畴。既言攸好德。乃锡之福。则攸好德。岂非贵耶。凶短折寿。与考终命之反。疾康宁之反。忧攸好德之反。贫富之反。而恶包于凶。弱包于短折。
福极相对。亦可以一义看。寿与凶短折相对。富与贫相对。宁与疾相对。攸好德与恶弱相对。康与忧相对。而考终命。包于寿。
寿富康宁考终命。全五行之气。攸好德。全五行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