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x 页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明皋徐滢修汝琳 著)
讲义
讲义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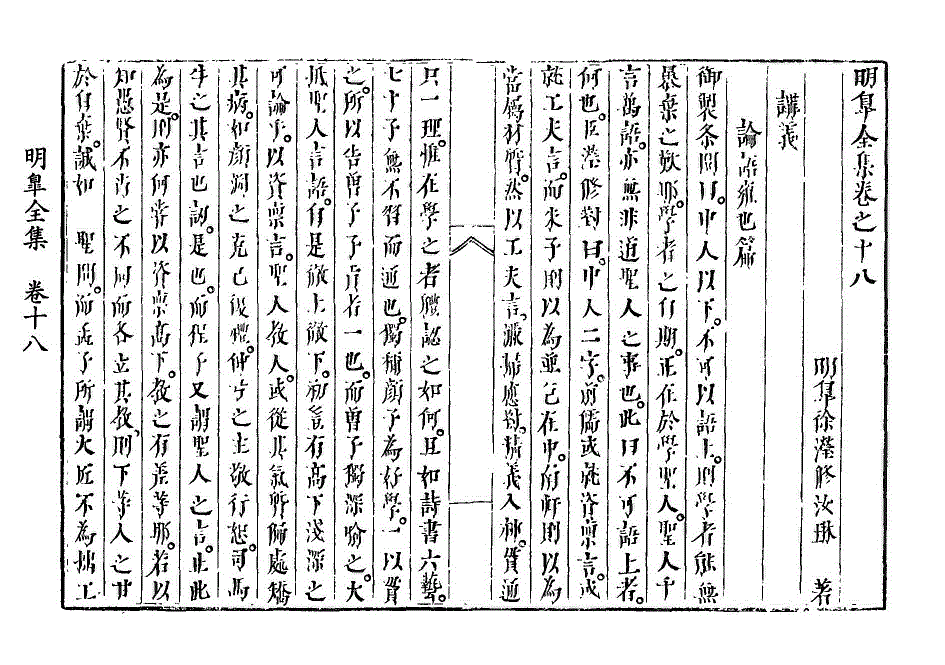 论语雍也篇
论语雍也篇御制条问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则学者能无暴弃之叹耶。学者之自期。正在于学圣人。圣人千言万语。亦无非道圣人之事也。此曰不可语上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中人二字。前儒或就资禀言。或就工夫言。而朱子则以为并包在中。南轩则以为当属材质。然以工夫言。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惟在学之者体认之如何。且如诗书六艺。七十子无不习而通也。独称颜子为好学。一以贯之。所以告曾子子贡者一也。而曾子独深喻之。大抵圣人言语。自是彻上彻下。初岂有高下浅深之可论乎。以资禀言。圣人教人。或从其气质偏处矫其病。如颜渊之克己复礼。仲弓之主敬行恕。司马牛之其言也讱。是也。而程子又谓圣人之言。止此为是。则亦何尝以资禀高下。教之有差等耶。若以知愚贤不肖之不同而各立其教。则下等人之甘于自弃。诚如 圣问。而孟子所谓大匠不为拙工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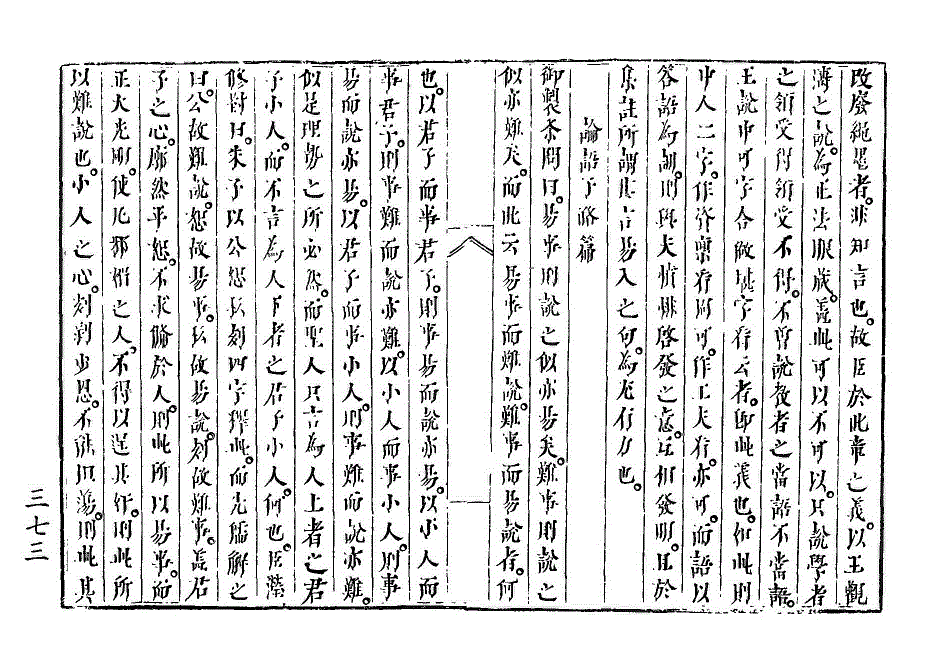 改废绳墨者。非知言也。故臣于此章之义。以王观涛之说。为正法眼藏。盖此可以不可以。只说学者之领受得领受不得。不曾说教者之当语不当语。王说中可字合做堪字看云者。即此义也。如此则中人二字。作资禀看固可。作工夫看。亦可。而语以答语为训。则与夫愤悱启发之意。互相发明。且于集注所谓其言易入之句。为尤有力也。
改废绳墨者。非知言也。故臣于此章之义。以王观涛之说。为正法眼藏。盖此可以不可以。只说学者之领受得领受不得。不曾说教者之当语不当语。王说中可字合做堪字看云者。即此义也。如此则中人二字。作资禀看固可。作工夫看。亦可。而语以答语为训。则与夫愤悱启发之意。互相发明。且于集注所谓其言易入之句。为尤有力也。论语子路篇
御制条问曰。易事则说之似亦易矣。难事则说之似亦难矣。而此云易事而难说。难事而易说者。何也。以君子而事君子。则事易而说亦易。以小人而事君子。则事难而说亦难。以小人而事小人。则事易而说亦易。以君子而事小人。则事难而说亦难。似是理势之所必然。而圣人只言为人上者之君子小人。而不言为人下者之君子小人。何也。臣滢修对曰。朱子以公恕私刻四字释此。而先儒解之曰。公故难说。恕故易事。私故易说。刻故难事。盖君子之心。廓然平恕。不求备于人。则此所以易事。而正大光明。使凡邪媚之人。不得以逞其奸。则此所以难说也。小人之心。刻剥少恩。不能坦荡。则此其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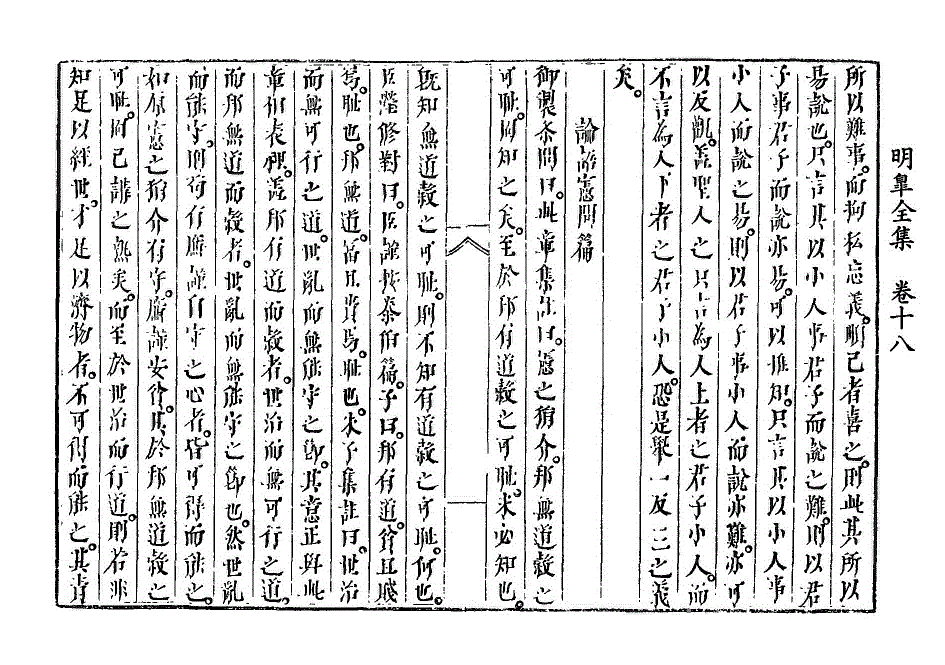 所以难事。而拘私忘义。顺己者喜之。则此其所以易说也。只言其以小人事君子而说之难。则以君子事君子而说亦易。可以推知。只言其以小人事小人而说之易。则以君子事小人而说亦难。亦可以反观。盖圣人之只言为人上者之君子小人。而不言为人下者之君子小人。恐是举一反三之义矣。
所以难事。而拘私忘义。顺己者喜之。则此其所以易说也。只言其以小人事君子而说之难。则以君子事君子而说亦易。可以推知。只言其以小人事小人而说之易。则以君子事小人而说亦难。亦可以反观。盖圣人之只言为人上者之君子小人。而不言为人下者之君子小人。恐是举一反三之义矣。论语宪问篇
御制条问曰。此章集注曰。宪之狷介。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未必知也。既知无道谷之可耻。则不知有道谷之可耻。何也。臣滢修对曰。臣谨按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朱子集注曰。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其意正与此章相表里。盖邦有道而谷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而邦无道而谷者。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也。然世乱而能守。则苟有廉谨自守之心者。皆可得而能之。如原宪之狷介有守。廉谨安贫。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已讲之熟矣。而至于世治而行道。则若非知足以经世。才足以济物者。不可得而能之。其责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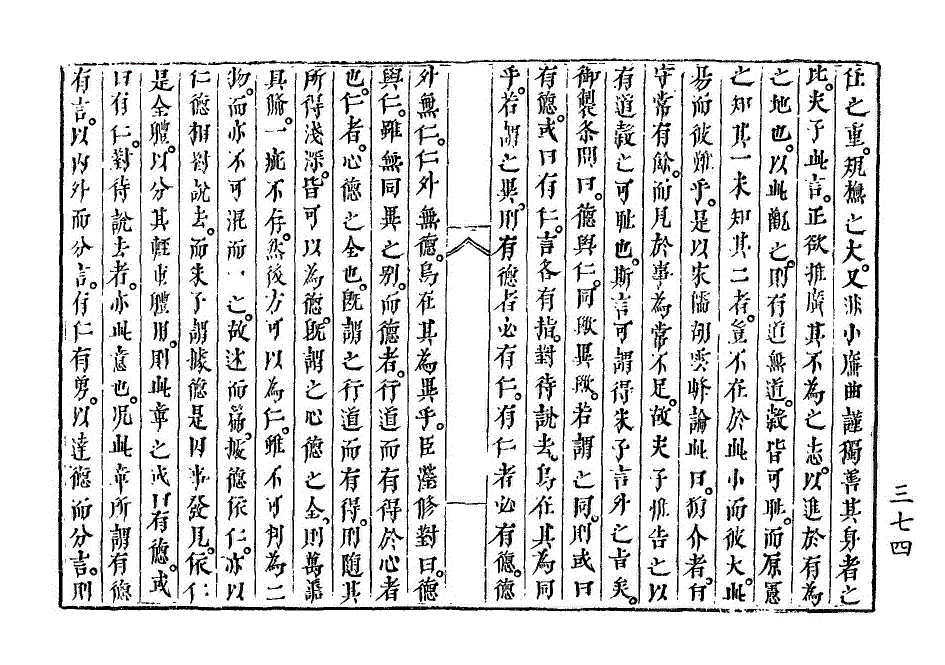 任之重。规模之大。又非小廉曲谨独善其身者之比。夫子此言。正欲推广其不为之志。以进于有为之地也。以此观之。则有道无道。谷皆可耻。而原宪之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岂不在于此小而彼大。此易而彼难乎。是以宋儒胡云峰论此曰。狷介者。自守常有馀。而见于事为常不足。故夫子惟告之以有道谷之可耻也。斯言可谓得朱子言外之旨矣。御制条问曰。德与仁。同欤异欤。若谓之同。则或曰有德。或曰有仁。言各有指。对待说去。乌在其为同乎。若谓之异。则有德者必有仁。有仁者必有德。德外无仁。仁外无德。乌在其为异乎。臣滢修对曰。德与仁。虽无同异之别。而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既谓之行道而有得。则随其所得浅深。皆可以为德。既谓之心德之全。则万善具备。一疵不存。然后方可以为仁。虽不可判为二物。而亦不可混而一之。故述而篇。据德依仁。亦以仁德相对说去。而朱子谓据德是因事发见。依仁是全体。以分其轻重体用。则此章之或曰有德。或曰有仁。对待说去者。亦此意也。况此章所谓有德有言。以内外而分言。有仁有勇。以达德而分言。则
任之重。规模之大。又非小廉曲谨独善其身者之比。夫子此言。正欲推广其不为之志。以进于有为之地也。以此观之。则有道无道。谷皆可耻。而原宪之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岂不在于此小而彼大。此易而彼难乎。是以宋儒胡云峰论此曰。狷介者。自守常有馀。而见于事为常不足。故夫子惟告之以有道谷之可耻也。斯言可谓得朱子言外之旨矣。御制条问曰。德与仁。同欤异欤。若谓之同。则或曰有德。或曰有仁。言各有指。对待说去。乌在其为同乎。若谓之异。则有德者必有仁。有仁者必有德。德外无仁。仁外无德。乌在其为异乎。臣滢修对曰。德与仁。虽无同异之别。而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既谓之行道而有得。则随其所得浅深。皆可以为德。既谓之心德之全。则万善具备。一疵不存。然后方可以为仁。虽不可判为二物。而亦不可混而一之。故述而篇。据德依仁。亦以仁德相对说去。而朱子谓据德是因事发见。依仁是全体。以分其轻重体用。则此章之或曰有德。或曰有仁。对待说去者。亦此意也。况此章所谓有德有言。以内外而分言。有仁有勇。以达德而分言。则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5H 页
 德在言先。仁在勇上。各有攸当。而既言有德有言。以见其口给之外饰。不如英华之积中。又从其德之在中者而分言仁与勇。以见其血气之勇。又不如全德之仁。尤可见仁与德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对待说去之中。德外无仁。仁外无德之意。自见于言外矣。 御制条问曰。管仲即一假仁者也。孔子未尝以仁轻许于人。而至于假仁之管仲。则再言如其仁而深许之者。何也。未得为仁人而有仁之功。果如集注所论。则管仲非仁人也。既非仁人。则虽有仁之功。恐不足许。而不但许之而已。必再言而深许之。何其与孰不知礼之斥。太相反耶。臣滢修对曰。仁。有以德而言者。有以功而言者。以德而言。则非心无私而事当理者。不可以当之。以功而言。则苟泽及人而惠推远者。亦可以当之。管仲之纠合诸侯。不假威力。虽是假仁之事。而尊攘之功。惠泽之博。是亦仁者之功效矣。然则以德而言仁。不可轻许于人。而以功而言仁。亦可重许于管仲。故集注既言管仲非仁人一句。以明夫子之深许者。不在于全体之仁。而又言有仁之功一句。以明管仲之仁。全在于利泽之及人。则此章之仁。与
德在言先。仁在勇上。各有攸当。而既言有德有言。以见其口给之外饰。不如英华之积中。又从其德之在中者而分言仁与勇。以见其血气之勇。又不如全德之仁。尤可见仁与德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对待说去之中。德外无仁。仁外无德之意。自见于言外矣。 御制条问曰。管仲即一假仁者也。孔子未尝以仁轻许于人。而至于假仁之管仲。则再言如其仁而深许之者。何也。未得为仁人而有仁之功。果如集注所论。则管仲非仁人也。既非仁人。则虽有仁之功。恐不足许。而不但许之而已。必再言而深许之。何其与孰不知礼之斥。太相反耶。臣滢修对曰。仁。有以德而言者。有以功而言者。以德而言。则非心无私而事当理者。不可以当之。以功而言。则苟泽及人而惠推远者。亦可以当之。管仲之纠合诸侯。不假威力。虽是假仁之事。而尊攘之功。惠泽之博。是亦仁者之功效矣。然则以德而言仁。不可轻许于人。而以功而言仁。亦可重许于管仲。故集注既言管仲非仁人一句。以明夫子之深许者。不在于全体之仁。而又言有仁之功一句。以明管仲之仁。全在于利泽之及人。则此章之仁。与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5L 页
 以上诸章之仁。精粗不同。不啻皎如矣。又按语类曰。自周室之衰。以至于秦。世乱极矣。高祖一朝平定。自六朝以至于隋。世乱极矣。太宗一朝扫治。二君者。虽未可谓仁人。谓之无仁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以此观之。夫子之重许者。正是圣人不以人废功之意也。恐未必与孰不知礼之训。有所径庭矣。 御制条问曰。上达当用达字。下达亦言达字。何也。达字。自是好个字也。是以中庸所谓达道达德达天德者。论语所谓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所指而言。虽各不同。皆从君子边说。而此外达字之见于经传者。莫非好题目。则此达字。恐不宜用于日趋污下之小人。而夫子之言如此。须无谓已有朱子及诸儒说而明辨之。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字书曰达。通也。从幸从走。盖达字。有穷到极至之意。故凡见于经传者。皆从君子边说。为其穷究到底。止于至善之地。非如仁与义之必其有定名而不可移也。若夫论语在邦必达之达。孟子达不离道之达。礼记推贤而进达之达。皆有通显之意。则所指不同。而且以中庸之达道达德言之。道与德。是主也。两达字。是宾也。道与德。是实字也。两达
以上诸章之仁。精粗不同。不啻皎如矣。又按语类曰。自周室之衰。以至于秦。世乱极矣。高祖一朝平定。自六朝以至于隋。世乱极矣。太宗一朝扫治。二君者。虽未可谓仁人。谓之无仁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以此观之。夫子之重许者。正是圣人不以人废功之意也。恐未必与孰不知礼之训。有所径庭矣。 御制条问曰。上达当用达字。下达亦言达字。何也。达字。自是好个字也。是以中庸所谓达道达德达天德者。论语所谓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所指而言。虽各不同。皆从君子边说。而此外达字之见于经传者。莫非好题目。则此达字。恐不宜用于日趋污下之小人。而夫子之言如此。须无谓已有朱子及诸儒说而明辨之。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字书曰达。通也。从幸从走。盖达字。有穷到极至之意。故凡见于经传者。皆从君子边说。为其穷究到底。止于至善之地。非如仁与义之必其有定名而不可移也。若夫论语在邦必达之达。孟子达不离道之达。礼记推贤而进达之达。皆有通显之意。则所指不同。而且以中庸之达道达德言之。道与德。是主也。两达字。是宾也。道与德。是实字也。两达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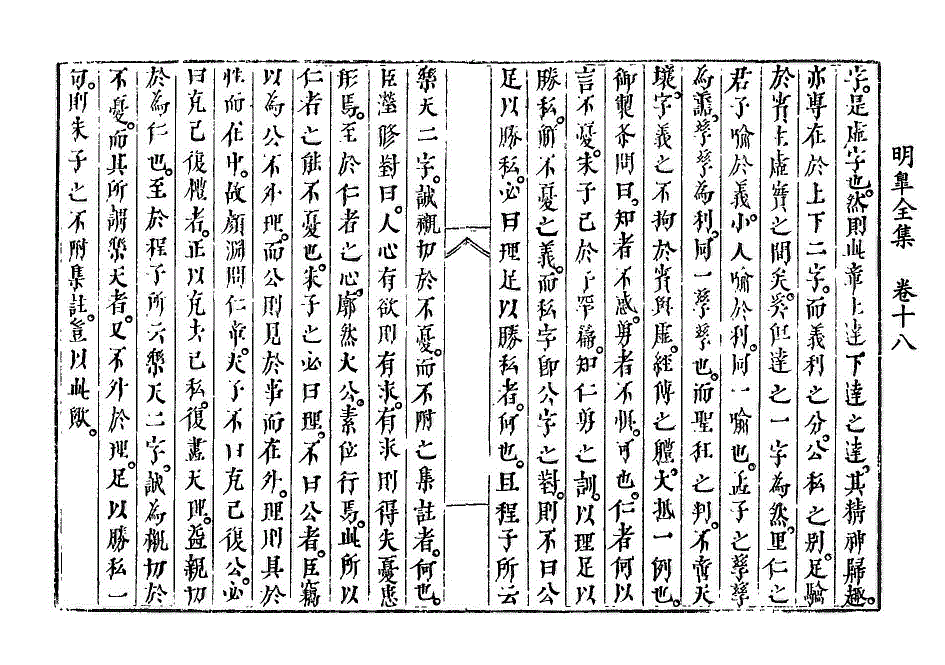 字。是虚字也。然则此章上达下达之达。其精神归趣。亦专在于上下二字。而义利之分。公私之别。足验于宾主虚实之间矣。奚但达之一字为然。里仁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一喻也。孟子之孳孳为善。孳孳为利。同一孳孳也。而圣狂之判。不啻天壤。字义之不拘于宾与虚。经传之体。大抵一例也。御制条问曰。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可也。仁者何以言不忧。朱子已于子罕篇。知仁勇之训。以理足以胜私。解不忧之义。而私字即公字之对。则不曰公足以胜私。必曰理足以胜私者。何也。且程子所云乐天二字。诚衬切于不忧。而不附之集注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人心有欲则有求。有求则得失忧患形焉。至于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素位行焉。此所以仁者之能不忧也。朱子之必曰理。不曰公者。臣窃以为公不外理。而公则见于事而在外。理则具于性而在中。故颜渊问仁章。夫子不曰克己复公。必曰克己复礼者。正以克去己私。复尽天理。益亲切于为仁也。至于程子所云乐天二字。诚为衬切于不忧。而其所谓乐天者。又不外于理。足以胜私一句。则朱子之不附集注。岂以此欤。
字。是虚字也。然则此章上达下达之达。其精神归趣。亦专在于上下二字。而义利之分。公私之别。足验于宾主虚实之间矣。奚但达之一字为然。里仁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一喻也。孟子之孳孳为善。孳孳为利。同一孳孳也。而圣狂之判。不啻天壤。字义之不拘于宾与虚。经传之体。大抵一例也。御制条问曰。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可也。仁者何以言不忧。朱子已于子罕篇。知仁勇之训。以理足以胜私。解不忧之义。而私字即公字之对。则不曰公足以胜私。必曰理足以胜私者。何也。且程子所云乐天二字。诚衬切于不忧。而不附之集注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人心有欲则有求。有求则得失忧患形焉。至于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素位行焉。此所以仁者之能不忧也。朱子之必曰理。不曰公者。臣窃以为公不外理。而公则见于事而在外。理则具于性而在中。故颜渊问仁章。夫子不曰克己复公。必曰克己复礼者。正以克去己私。复尽天理。益亲切于为仁也。至于程子所云乐天二字。诚为衬切于不忧。而其所谓乐天者。又不外于理。足以胜私一句。则朱子之不附集注。岂以此欤。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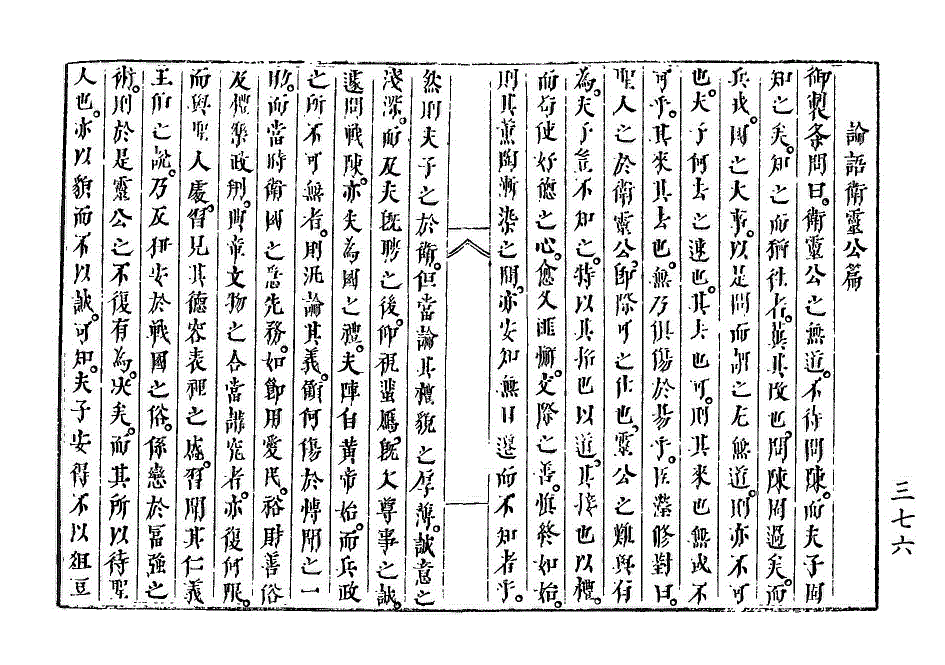 论语卫灵公篇
论语卫灵公篇御制条问曰。卫灵公之无道。不待问陈。而夫子固知之矣。知之而犹往者。冀其改也。问陈固过矣。而兵戎。国之大事。以是问而谓之尤无道。则亦不可也。夫子何去之速也。其去也可。则其来也无或不可乎。其来其去也。无乃俱伤于易乎。臣滢修对曰。圣人之于卫灵公。即际可之仕也。灵公之难与有为。夫子岂不知之。特以其招也以道。其接也以礼。而苟使好德之心。愈久匪懈。交际之善。慎终如始。则其薰陶渐染之间。亦安知无日迁而不知者乎。然则夫子之于卫。但当论其礼貌之厚薄。诚意之浅深。而及夫既聘之后。仰视蜚雁。既欠尊事之诚。遽问战陈。亦失为国之礼。夫阵自黄帝始。而兵政之所不可无者。则汎论其义。顾何伤于博闻之一助。而当时卫国之急先务。如节用爱民。裕财善俗及礼乐政刑。典章文物之合当讲究者。亦复何限。而与圣人处。习见其德容表里之盛。习闻其仁义王伯之说。乃反狃安于战国之俗。系恋于富强之术。则于是灵公之不复有为。决矣。而其所以待圣人也。亦以貌而不以诚。可知。夫子安得不以俎豆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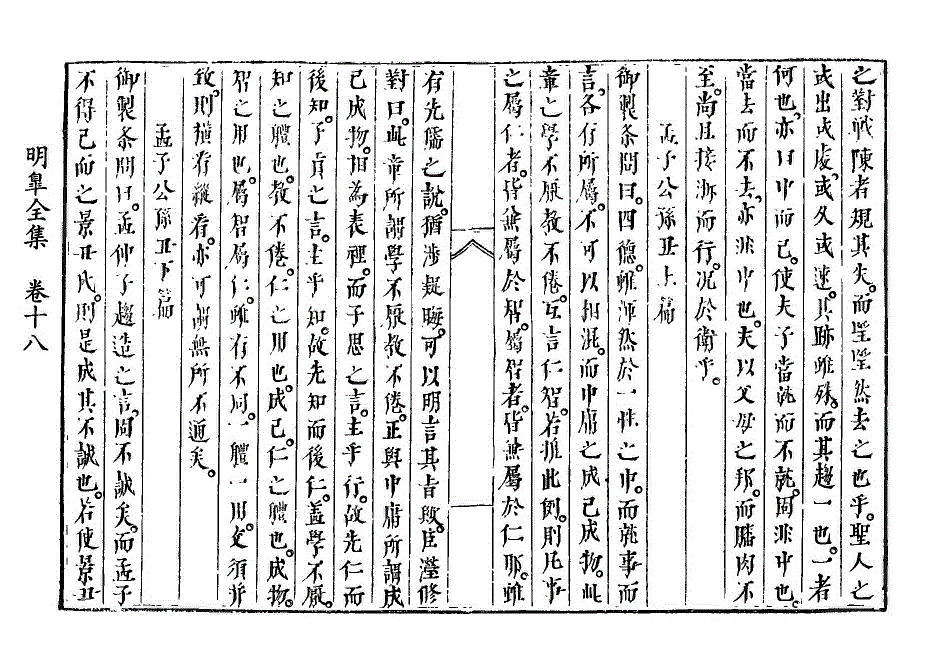 之对战陈者规其失。而望望然去之也乎。圣人之或出或处。或久或速。其迹虽殊。而其趋一也。一者何也。亦曰中而已。使夫子当就而不就。固非中也。当去而不去。亦非中也。夫以父母之邦。而膰肉不至。尚且接浙而行。况于卫乎。
之对战陈者规其失。而望望然去之也乎。圣人之或出或处。或久或速。其迹虽殊。而其趋一也。一者何也。亦曰中而已。使夫子当就而不就。固非中也。当去而不去。亦非中也。夫以父母之邦。而膰肉不至。尚且接浙而行。况于卫乎。孟子公孙丑上篇
御制条问曰。四德。虽浑然于一性之中。而就事而言。各有所属。不可以相混。而中庸之成己成物。此章之学不厌教不倦。互言仁智。若推此例。则凡事之属仁者。皆兼属于智。属智者。皆兼属于仁耶。虽有先儒之说。犹涉疑晦。可以明言其旨欤。臣滢修对曰。此章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正与中庸所谓成己成物。相为表里。而子思之言。主乎行。故先仁而后知。子贡之言。主乎知。故先知而后仁。盖学不厌。知之体也。教不倦。仁之用也。成己。仁之体也。成物。智之用也。属智属仁。虽有不同。一体一用。交须并致。则横看纵看。亦可谓无所不通矣。
孟子公孙丑下篇
御制条问曰。孟仲子趋造之言。固不诚矣。而孟子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则是成其不诚也。若使景丑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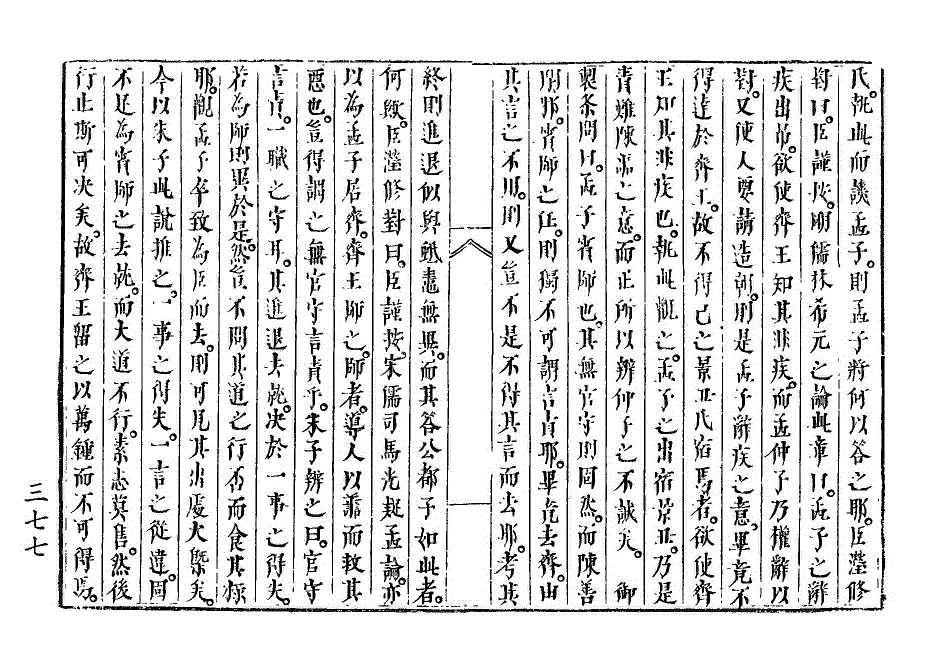 氏。执此而讥孟子。则孟子将何以答之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明儒林希元之论此章曰。孟子之辞疾出吊。欲使齐王知其非疾。而孟仲子乃权辞以对。又使人要请造朝。则是孟子辞疾之意。毕竟不得达于齐王。故不得已之景丑氏宿焉者。欲使齐王知其非疾也。执此观之。孟子之出宿景丑。乃是责难陈善之意。而正所以辨仲子之不诚矣。 御制条问曰。孟子宾师也。其无官守则固然。而陈善闲邪。宾师之任。则独不可谓言责耶。毕竟去齐。由其言之不用。则又岂不是不得其言而去耶。考其终则进退似与蚳蛙无异。而其答公都子如此者。何欤。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宋儒司马光疑孟论。亦以为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也。岂得谓之无官守言责乎。朱子辨之曰。官守言责。一职之守耳。其进退去就。决于一事之得失。若为师则异于是。然岂不问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禄耶。观孟子卒致为臣而去。则可见其出处大槩矣。今以朱子此说推之。一事之得失。一言之从违。固不足为宾师之去就。而大道不行。素志莫售。然后行止斯可决矣。故齐王留之以万钟而不可得焉。
氏。执此而讥孟子。则孟子将何以答之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明儒林希元之论此章曰。孟子之辞疾出吊。欲使齐王知其非疾。而孟仲子乃权辞以对。又使人要请造朝。则是孟子辞疾之意。毕竟不得达于齐王。故不得已之景丑氏宿焉者。欲使齐王知其非疾也。执此观之。孟子之出宿景丑。乃是责难陈善之意。而正所以辨仲子之不诚矣。 御制条问曰。孟子宾师也。其无官守则固然。而陈善闲邪。宾师之任。则独不可谓言责耶。毕竟去齐。由其言之不用。则又岂不是不得其言而去耶。考其终则进退似与蚳蛙无异。而其答公都子如此者。何欤。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宋儒司马光疑孟论。亦以为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也。岂得谓之无官守言责乎。朱子辨之曰。官守言责。一职之守耳。其进退去就。决于一事之得失。若为师则异于是。然岂不问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禄耶。观孟子卒致为臣而去。则可见其出处大槩矣。今以朱子此说推之。一事之得失。一言之从违。固不足为宾师之去就。而大道不行。素志莫售。然后行止斯可决矣。故齐王留之以万钟而不可得焉。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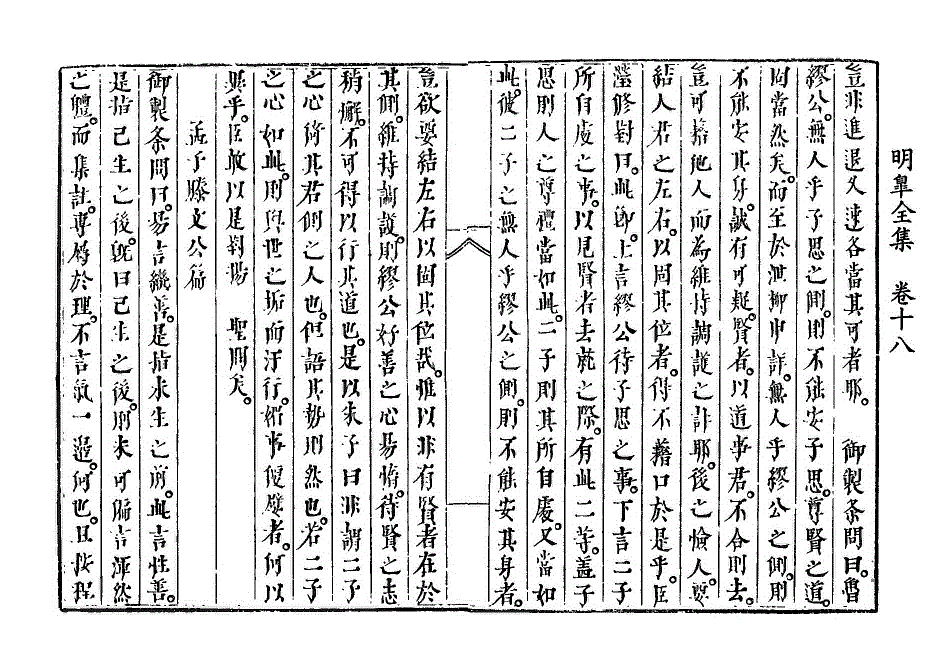 岂非进退久速各当其可者耶。 御制条问曰。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尊贤之道。固当然矣。而至于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诚有可疑。贤者。以道事君。不合则去。岂可藉他人而为维持调护之计耶。后之憸人。要结人君之左右。以固其位者。得不藉口于是乎。臣滢修对曰。此节。上言缪公待子思之事。下言二子所自处之事。以见贤者去就之际。有此二等。盖子思则人之尊礼当如此。二子则其所自处。又当如此。彼二子之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者。岂欲要结左右以固其位哉。惟以非有贤者在于其侧。维持调护。则缪公好善之心易惰。待贤之志稍懈。不可得以行其道也。是以朱子曰非谓二子之心倚其君侧之人也。但语其势则然也。若二子之心如此。则与世之垢面污行。媚事便嬖者。何以异乎。臣敢以是对扬 圣问矣。
岂非进退久速各当其可者耶。 御制条问曰。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尊贤之道。固当然矣。而至于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诚有可疑。贤者。以道事君。不合则去。岂可藉他人而为维持调护之计耶。后之憸人。要结人君之左右。以固其位者。得不藉口于是乎。臣滢修对曰。此节。上言缪公待子思之事。下言二子所自处之事。以见贤者去就之际。有此二等。盖子思则人之尊礼当如此。二子则其所自处。又当如此。彼二子之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者。岂欲要结左右以固其位哉。惟以非有贤者在于其侧。维持调护。则缪公好善之心易惰。待贤之志稍懈。不可得以行其道也。是以朱子曰非谓二子之心倚其君侧之人也。但语其势则然也。若二子之心如此。则与世之垢面污行。媚事便嬖者。何以异乎。臣敢以是对扬 圣问矣。孟子滕文公篇
御制条问曰。易言继善。是指未生之前。此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既曰已生之后。则未可偏言浑然之体。而集注。专属于理。不言气一边。何也。且按程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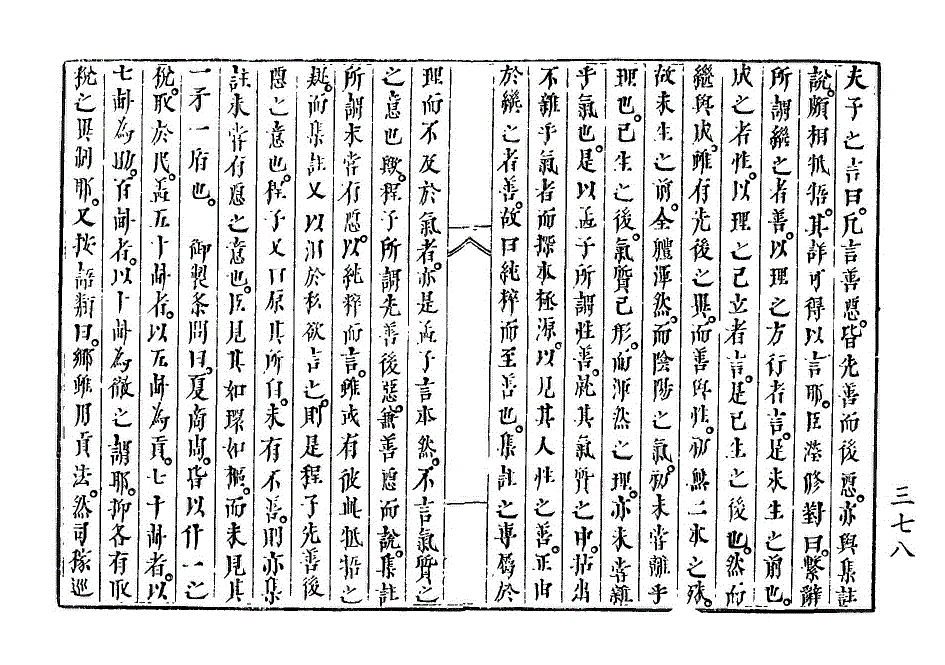 夫子之言曰。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亦与集注说。颇相牴牾。其详可得以言耶。臣滢修对曰。系辞所谓继之者善。以理之方行者言。是未生之前也。成之者性。以理之已立者言。是已生之后也。然而继与成。虽有先后之异。而善与性。初无二本之殊。故未生之前。全体浑然。而阴阳之气。初未尝离乎理也。已生之后。气质已形。而浑然之理。亦未尝杂乎气也。是以孟子所谓性善。就其气质之中。拈出不杂乎气者而探本极源。以见其人性之善。正由于继之者善。故曰纯粹而至善也。集注之专属于理而不及于气者。亦是孟子言本然。不言气质之之意也欤。程子所谓先善后恶。兼善恶而说。集注所谓未尝有恶。以纯粹而言。虽或有彼此牴牾之疑。而集注又以汩于私欲言之。则是程子先善后恶之意也。程子又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则亦集注未尝有恶之意也。臣见其如环如枢。而未见其一矛一盾也。 御制条问曰。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税。取于民。盖五十亩者。以五亩为贡。七十亩者。以七亩为助。百亩者。以十亩为彻之谓耶。抑各有取税之异制耶。又按语类曰。乡虽用贡法。然司稼巡
夫子之言曰。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亦与集注说。颇相牴牾。其详可得以言耶。臣滢修对曰。系辞所谓继之者善。以理之方行者言。是未生之前也。成之者性。以理之已立者言。是已生之后也。然而继与成。虽有先后之异。而善与性。初无二本之殊。故未生之前。全体浑然。而阴阳之气。初未尝离乎理也。已生之后。气质已形。而浑然之理。亦未尝杂乎气也。是以孟子所谓性善。就其气质之中。拈出不杂乎气者而探本极源。以见其人性之善。正由于继之者善。故曰纯粹而至善也。集注之专属于理而不及于气者。亦是孟子言本然。不言气质之之意也欤。程子所谓先善后恶。兼善恶而说。集注所谓未尝有恶。以纯粹而言。虽或有彼此牴牾之疑。而集注又以汩于私欲言之。则是程子先善后恶之意也。程子又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则亦集注未尝有恶之意也。臣见其如环如枢。而未见其一矛一盾也。 御制条问曰。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税。取于民。盖五十亩者。以五亩为贡。七十亩者。以七亩为助。百亩者。以十亩为彻之谓耶。抑各有取税之异制耶。又按语类曰。乡虽用贡法。然司稼巡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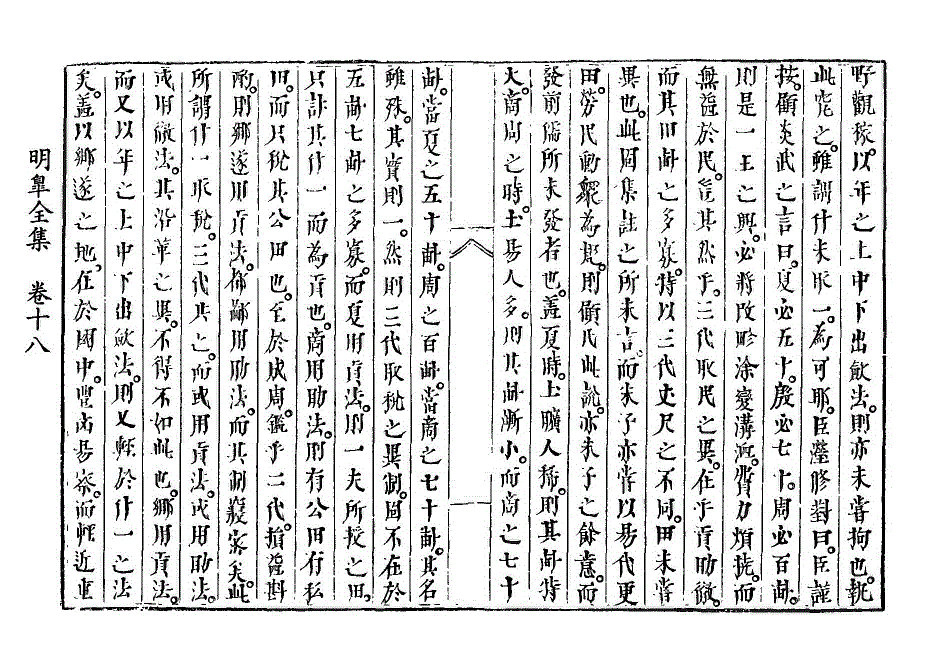 野观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亦未尝拘也。执此究之。虽谓什未取一。为可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顾炎武之言曰。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亩。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费力烦挠。而无益于民。岂其然乎。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其田亩之多寡。特以三代丈尺之不同。田未尝异也。此固集注之所未言。而朱子亦尝以易代更田。劳民动众为疑。则顾氏此说。亦朱子之馀意。而发前儒所未发者也。盖夏时。土旷人稀。则其亩特大。商周之时。土易人多。则其亩渐小。而商之七十亩。当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当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殊。其实则一。然则三代取税之异制。固不在于五亩七亩之多寡。而夏用贡法。则一夫所授之田。只计其什一而为贡也。商用助法。则有公田有私田。而只税其公田也。至于成周。鉴乎二代。损益斟酌。则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而其制寝密矣。此所谓什一取税。三代共之。而或用贡法。或用助法。或用彻法。其沿革之异。不得不如此也。乡用贡法。而又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又轻于什一之法矣。盖以乡遂之地。在于国中。礼凶易察。而轻近重
野观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亦未尝拘也。执此究之。虽谓什未取一。为可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顾炎武之言曰。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亩。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费力烦挠。而无益于民。岂其然乎。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其田亩之多寡。特以三代丈尺之不同。田未尝异也。此固集注之所未言。而朱子亦尝以易代更田。劳民动众为疑。则顾氏此说。亦朱子之馀意。而发前儒所未发者也。盖夏时。土旷人稀。则其亩特大。商周之时。土易人多。则其亩渐小。而商之七十亩。当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当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殊。其实则一。然则三代取税之异制。固不在于五亩七亩之多寡。而夏用贡法。则一夫所授之田。只计其什一而为贡也。商用助法。则有公田有私田。而只税其公田也。至于成周。鉴乎二代。损益斟酌。则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而其制寝密矣。此所谓什一取税。三代共之。而或用贡法。或用助法。或用彻法。其沿革之异。不得不如此也。乡用贡法。而又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又轻于什一之法矣。盖以乡遂之地。在于国中。礼凶易察。而轻近重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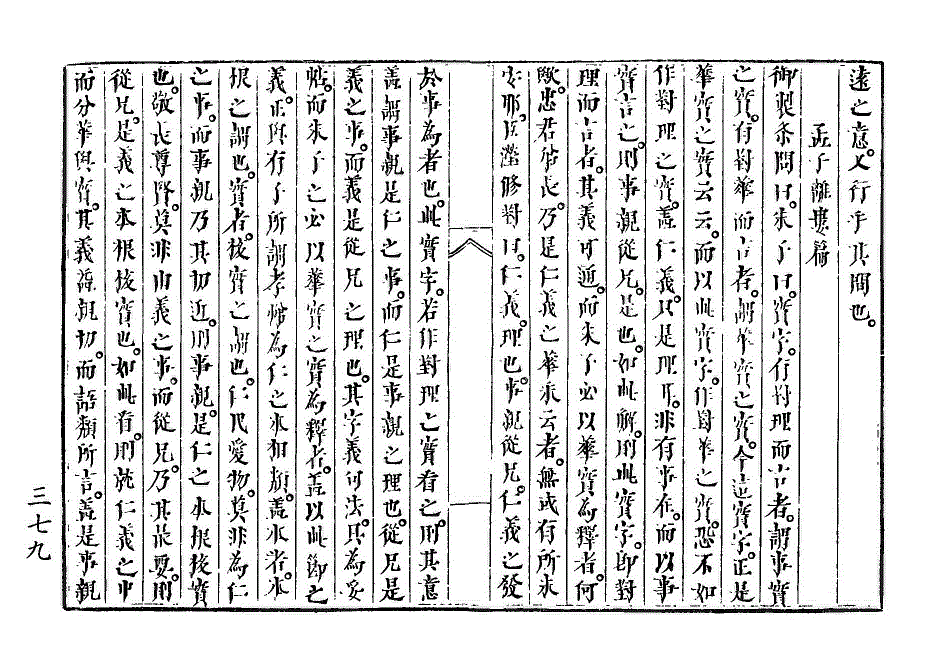 远之意。又行乎其间也。
远之意。又行乎其间也。孟子离娄篇
御制条问曰。朱子曰。实字。有对理而言者。谓事实之实。有对华而言者。谓华实之实。今这实字。正是华实之实云云。而以此实字。作对华之实。恐不如作对理之实。盖仁义。只是理耳。非有事在。而以事实言之。则事亲从兄。是也。如此解。则此实字。即对理而言者。其义可通。而朱子必以华实为释者。何欤。忠君弟长。乃是仁义之华采云者。无或有所未安耶。臣滢修对曰。仁义。理也。事亲从兄。仁义之发于事为者也。此实字。若作对理之实看之。则其意盖谓事亲是仁之事。而仁是事亲之理也。从兄是义之事。而义是从兄之理也。其字义句法。具为妥帖。而朱子之必以华实之实为释者。盖以此节之义。正与有子所谓孝悌为仁之本相类。盖本者。本根之谓也。实者。核实之谓也。仁民爱物。莫非为仁之事。而事亲乃其切近。则事亲。是仁之本根核实也。敬长尊贤。莫非由义之事。而从兄。乃其最要。则从兄。是义之本根核实也。如此看。则就仁义之中而分华与实。其义益亲切。而语类所言。盖是事亲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0H 页
 孝故事君忠。事兄弟故事长敬之意。而非真以忠君弟长为仁义之华采也。恐未必以是为疑也。
孝故事君忠。事兄弟故事长敬之意。而非真以忠君弟长为仁义之华采也。恐未必以是为疑也。孟子万章篇
御制条问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事舜于𤱶亩之中。欲察于夫妇间隐微之际。则二女以观其内。固圣人视人之道也。但同姓之百世不通婚。于礼则然。而尧以女妻之。按帝王世纪。舜乃尧之至亲也。以至亲而举以为婿。得无嫌于百世不通婚之礼耶。臣滢修对曰。自古通经考古之士。莫不以此为一大疑案。或以史记为据而言。舜是黄帝苗裔。则固与帝尧同族。而犹相婚姻者。是时仪文未备。礼节犹疏。同姓不婚之礼。实自成周以后也。或以国语为据而言。舜之系出于虞幕五帝之中。舜独不祖黄帝。初非帝尧之同姓也。至马骕作绎史。博考众说而折衷之曰。左传史趋之言云。自幕至于𥌒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为幕。审矣。史记之误。由于轻信世本之书。果如世本所言。黄帝至尧五世。而至舜则九世。颛顼至禹三世。而至舜▦九(则七)世。何舜独年代之数而尧禹年代之旷耶。臣则以为文献之徵信者。莫如经。而舜祖虞幕之说。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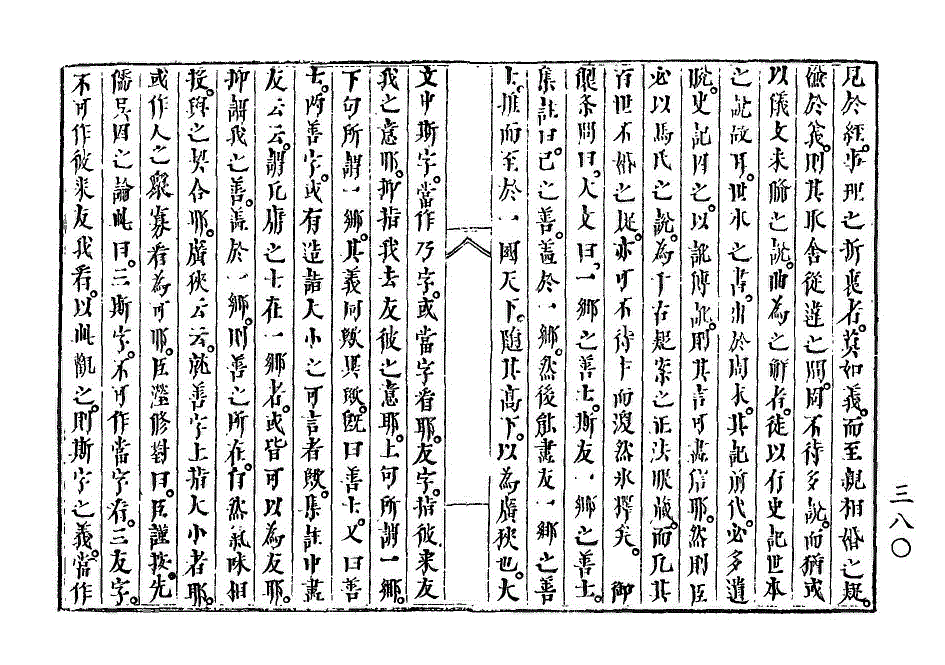 见于经。事理之折衷者。莫如义。而至亲相婚之疑。嫌于义。则其取舍从违之间。固不待多说。而犹或以仪文未备之说。曲为之解者。徒以有史记世本之说故耳。世本之书。出于周末。其记前代。必多遗脱。史记因之。以讹传讹。则其言可尽信耶。然则臣必以马氏之说。为千古疑案之正法眼藏。而凡其百世不婚之疑。亦可不待卞而涣然冰释矣。 御制条问曰。大文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集注曰。己之善。盖于一乡。然后能尽友一乡之善士。推而至于一国天下。随其高下。以为广狭也。大文中斯字。当作乃字。或当字看耶。友字。指彼来友我之意耶。抑指我去友彼之意耶。上句所谓一乡。下句所谓一乡。其义同欤异欤。既曰善士。又曰善士。两善字。或有造诣大小之可言者欤。集注中尽友云云。谓凡庸之士在一乡者。或皆可以为友耶。抑谓我之善。盖于一乡。则善之所在。自然气味相投。与之契合耶。广狭云云。就善字上指大小者耶。或作人之众寡看为可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先儒吴因之论此曰。三斯字。不可作当字看。三友字。不可作彼来友我看。以此观之。则斯字之义。当作
见于经。事理之折衷者。莫如义。而至亲相婚之疑。嫌于义。则其取舍从违之间。固不待多说。而犹或以仪文未备之说。曲为之解者。徒以有史记世本之说故耳。世本之书。出于周末。其记前代。必多遗脱。史记因之。以讹传讹。则其言可尽信耶。然则臣必以马氏之说。为千古疑案之正法眼藏。而凡其百世不婚之疑。亦可不待卞而涣然冰释矣。 御制条问曰。大文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集注曰。己之善。盖于一乡。然后能尽友一乡之善士。推而至于一国天下。随其高下。以为广狭也。大文中斯字。当作乃字。或当字看耶。友字。指彼来友我之意耶。抑指我去友彼之意耶。上句所谓一乡。下句所谓一乡。其义同欤异欤。既曰善士。又曰善士。两善字。或有造诣大小之可言者欤。集注中尽友云云。谓凡庸之士在一乡者。或皆可以为友耶。抑谓我之善。盖于一乡。则善之所在。自然气味相投。与之契合耶。广狭云云。就善字上指大小者耶。或作人之众寡看为可耶。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先儒吴因之论此曰。三斯字。不可作当字看。三友字。不可作彼来友我看。以此观之。则斯字之义。当作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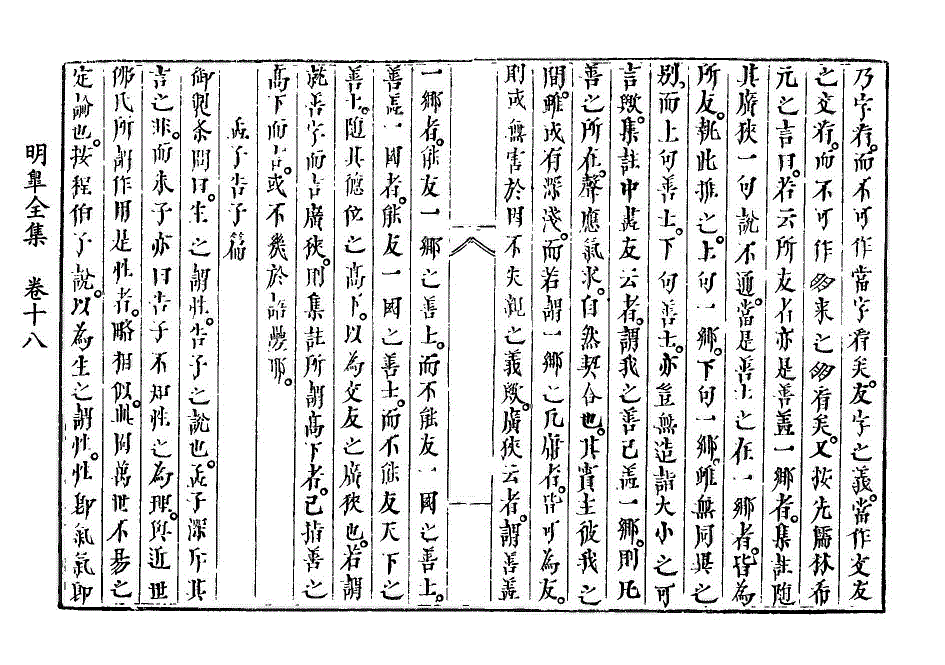 乃字看。而不可作当字看矣。友字之义。当作交友之交看。而不可作朋来之朋看矣。又按先儒林希元之言曰。若云所友者亦是善盖一乡者。集注随其广狭一句说不通。当是善士之在一乡者。皆为所友。执此推之。上句一乡。下句一乡。虽无同异之别。而上句善士。下句善士。亦岂无造诣大小之可言欤。集注中尽友云者。谓我之善已盖一乡。则凡善之所在。声应气求。自然契合也。其宾主彼我之间。虽或有深浅。而若谓一乡之凡庸者。皆可为友。则或无害于因不失亲之义欤。广狭云者。谓善盖一乡者。能友一乡之善士。而不能友一国之善士。善盖一国者。能友一国之善士。而不能友天下之善士。随其德位之高下。以为交友之广狭也。若谓就善字而言广狭。则集注所谓高下者。已指善之高下而言。或不几于语叠耶。
乃字看。而不可作当字看矣。友字之义。当作交友之交看。而不可作朋来之朋看矣。又按先儒林希元之言曰。若云所友者亦是善盖一乡者。集注随其广狭一句说不通。当是善士之在一乡者。皆为所友。执此推之。上句一乡。下句一乡。虽无同异之别。而上句善士。下句善士。亦岂无造诣大小之可言欤。集注中尽友云者。谓我之善已盖一乡。则凡善之所在。声应气求。自然契合也。其宾主彼我之间。虽或有深浅。而若谓一乡之凡庸者。皆可为友。则或无害于因不失亲之义欤。广狭云者。谓善盖一乡者。能友一乡之善士。而不能友一国之善士。善盖一国者。能友一国之善士。而不能友天下之善士。随其德位之高下。以为交友之广狭也。若谓就善字而言广狭。则集注所谓高下者。已指善之高下而言。或不几于语叠耶。孟子告子篇
御制条问曰。生之谓性。告子之说也。孟子深斥其言之非。而朱子亦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似。此固万世不易之定论也。按程伯子说。以为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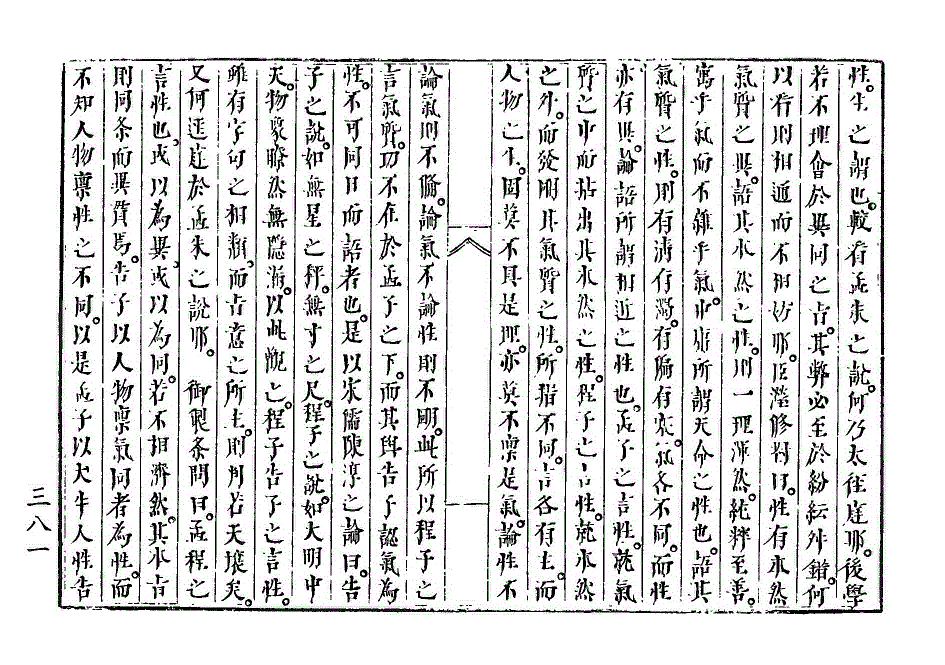 性。生之谓也。较看孟朱之说。何乃太径庭耶。后学若不理会于异同之旨。其弊必至于纷纭舛错。何以看则相通而不相妨耶。臣滢修对曰。性有本然气质之异。语其本然之性。则一理浑然。纯粹至善。寓乎气而不杂乎气。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也。语其气质之性。则有清有浊。有偏有塞。气各不同。而性亦有异。论语所谓相近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就气质之中而拈出其本然之性。程子之言性。就本然之外。而发明其气质之性。所指不同。言各有主。而人物之生。固莫不具是理。亦莫不禀是气。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此所以程子之言气质。功不在于孟子之下。而其与告子认气为性。不可同日而语者也。是以宋儒陈淳之论曰。告子之说。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程子之说。如大明中天。物象瞭然无隐漏。以此观之。程子告子之言性。虽有字句之相类。而旨意之所主。则判若天壤矣。又何径庭于孟朱之说耶。 御制条问曰。孟程之言性也。或以为异。或以为同。若不相济然。其本旨则同条而异贯焉。告子以人物禀气同者为性。而不知人物禀性之不同。以是孟子以犬牛人性告
性。生之谓也。较看孟朱之说。何乃太径庭耶。后学若不理会于异同之旨。其弊必至于纷纭舛错。何以看则相通而不相妨耶。臣滢修对曰。性有本然气质之异。语其本然之性。则一理浑然。纯粹至善。寓乎气而不杂乎气。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也。语其气质之性。则有清有浊。有偏有塞。气各不同。而性亦有异。论语所谓相近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就气质之中而拈出其本然之性。程子之言性。就本然之外。而发明其气质之性。所指不同。言各有主。而人物之生。固莫不具是理。亦莫不禀是气。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此所以程子之言气质。功不在于孟子之下。而其与告子认气为性。不可同日而语者也。是以宋儒陈淳之论曰。告子之说。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程子之说。如大明中天。物象瞭然无隐漏。以此观之。程子告子之言性。虽有字句之相类。而旨意之所主。则判若天壤矣。又何径庭于孟朱之说耶。 御制条问曰。孟程之言性也。或以为异。或以为同。若不相济然。其本旨则同条而异贯焉。告子以人物禀气同者为性。而不知人物禀性之不同。以是孟子以犬牛人性告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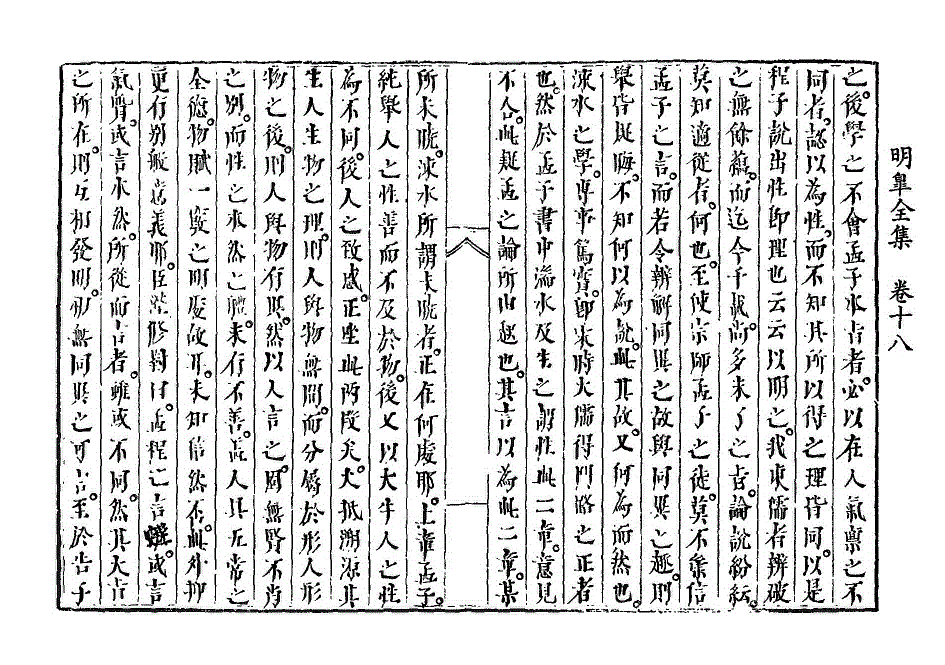 之。后学之不会孟子本旨者。必以在人气禀之不同者。认以为性。而不知其所以得之理皆同。以是程子说出性即理也云云以明之。我东儒者辨破之无馀蕴。而迄今千载。尚多未了之旨。论说纷纭。莫知适从者。何也。至使宗师孟子之徒。莫不崇信孟子之言。而若令辨解同异之故与同异之趣。则举皆疑晦。不知何以为说。此其故。又何为而然也。涑水之学。专事笃实。即宋时大儒得门路之正者也。然于孟子书中湍水及生之谓性此二章。意见不合。此疑孟之论所由起也。其言以为此二章。某所未晓。涑水所谓未晓者。正在何处耶。上章孟子。纯举人之性善而不及于物。后又以犬牛人之性为不同。后人之致惑。正坐此两段矣。大抵溯源其生人生物之理。则人与物无间。而分属于形人形物之后。则人与物有异。然以人言之。固无贤不肖之别。而性之本然之体。未有不善。盖人具五常之全德。物赋一窍之明处故耳。未知信然否。此外抑更有别般意义耶。臣滢修对曰。孟程之言▦。或言气质。或言本然。所从而言者。虽或不同。然其大旨之所在。则互相发明。初无同异之可言。至于告子
之。后学之不会孟子本旨者。必以在人气禀之不同者。认以为性。而不知其所以得之理皆同。以是程子说出性即理也云云以明之。我东儒者辨破之无馀蕴。而迄今千载。尚多未了之旨。论说纷纭。莫知适从者。何也。至使宗师孟子之徒。莫不崇信孟子之言。而若令辨解同异之故与同异之趣。则举皆疑晦。不知何以为说。此其故。又何为而然也。涑水之学。专事笃实。即宋时大儒得门路之正者也。然于孟子书中湍水及生之谓性此二章。意见不合。此疑孟之论所由起也。其言以为此二章。某所未晓。涑水所谓未晓者。正在何处耶。上章孟子。纯举人之性善而不及于物。后又以犬牛人之性为不同。后人之致惑。正坐此两段矣。大抵溯源其生人生物之理。则人与物无间。而分属于形人形物之后。则人与物有异。然以人言之。固无贤不肖之别。而性之本然之体。未有不善。盖人具五常之全德。物赋一窍之明处故耳。未知信然否。此外抑更有别般意义耶。臣滢修对曰。孟程之言▦。或言气质。或言本然。所从而言者。虽或不同。然其大旨之所在。则互相发明。初无同异之可言。至于告子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2L 页
 之言性。既不知性与气之分而认气为性。又不知气或不齐。性亦有异。混人物而无别。纷纭错杂。浑沦说去。其失正在于徒知知觉运动之气。人与物无异。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理。因其气之偏全。有发用之不同也。是以孟子以犬牛人性之说折之。其意精矣。然而后儒之不会本旨者。或有以所禀之气不同者。认以为性。而不知其所受之理无异。则又有程夫子性即理也之说矣。夫孟子之言如此。程子之论如此。其他宋明诸儒之发明推说。我东名贤之讨论辨释。无复馀蕴。而迄乎今。纷纭舛错。尚为不决之疑案者。岂有他哉。只缘读之者抉摘皮膜而无融会贯通之妙。因循蹈袭而无精切自得之见耳。虽以涑水之笃实正大。犹未免有疑。而至于李靓晁公武之徒。其说益肆。臣尝以疑孟论观之。则其所谓未晓者。在于湍水章。则以人无有不善之说为失言。于此章。则以白羽白雪之喻为辩。胜其言之误已。有余隐之辨论。臣何必架叠哉。御制条问曰。人性皆善。指理一之体也。人物不同。指气局之殊也。大抵孟子言性。就人言则专言是理。并与物言。则又不能遗是气焉。非孟子之言性。
之言性。既不知性与气之分而认气为性。又不知气或不齐。性亦有异。混人物而无别。纷纭错杂。浑沦说去。其失正在于徒知知觉运动之气。人与物无异。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理。因其气之偏全。有发用之不同也。是以孟子以犬牛人性之说折之。其意精矣。然而后儒之不会本旨者。或有以所禀之气不同者。认以为性。而不知其所受之理无异。则又有程夫子性即理也之说矣。夫孟子之言如此。程子之论如此。其他宋明诸儒之发明推说。我东名贤之讨论辨释。无复馀蕴。而迄乎今。纷纭舛错。尚为不决之疑案者。岂有他哉。只缘读之者抉摘皮膜而无融会贯通之妙。因循蹈袭而无精切自得之见耳。虽以涑水之笃实正大。犹未免有疑。而至于李靓晁公武之徒。其说益肆。臣尝以疑孟论观之。则其所谓未晓者。在于湍水章。则以人无有不善之说为失言。于此章。则以白羽白雪之喻为辩。胜其言之误已。有余隐之辨论。臣何必架叠哉。御制条问曰。人性皆善。指理一之体也。人物不同。指气局之殊也。大抵孟子言性。就人言则专言是理。并与物言。则又不能遗是气焉。非孟子之言性。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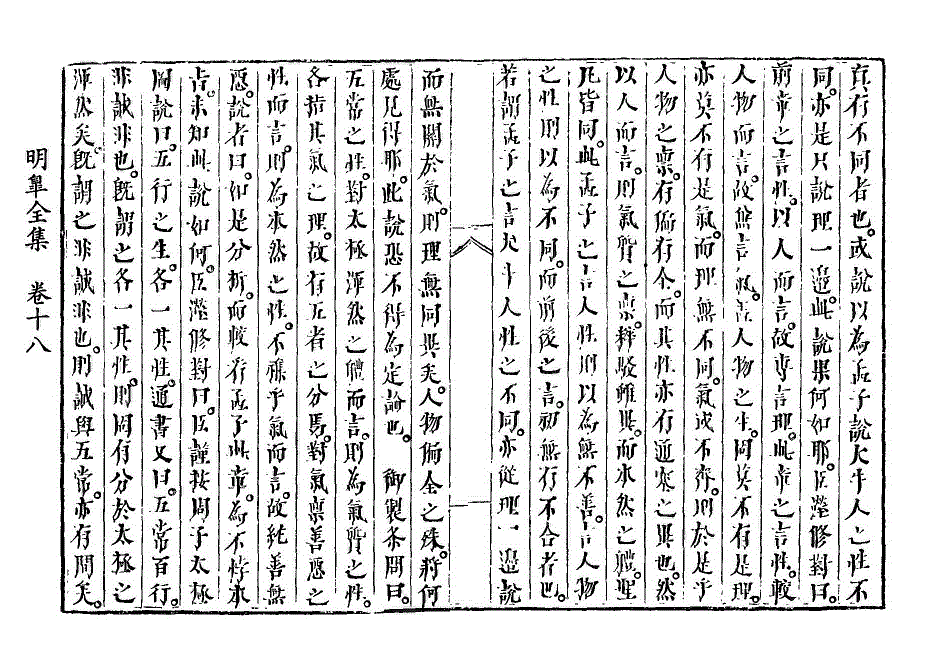 真有不同者也。或说以为孟子说犬牛人之性不同。亦是只说理一边。此说果何如耶。臣滢修对曰。前章之言性。以人而言。故专言理。此章之言性。较人物而言。故兼言气。盖人物之生。固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气。而理无不同。气或不齐。则于是乎人物之禀。有偏有全。而其性亦有通塞之异也。然以人而言。则气质之禀。粹驳虽异。而本然之体。圣凡皆同。此孟子之言人性则以为无不善。言人物之性则以为不同。而前后之言。初无有不合者也。若谓孟子之言犬牛人性之不同。亦从理一边说而无关于气。则理无同异矣。人物偏全之殊。将何处见得耶。此说恐不得为定论也。 御制条问曰。五常之性。对太极浑然之体而言。则为气质之性。各指其气之理。故有五者之分焉。对气禀善恶之性而言。则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而言。故纯善无恶。说者曰。如是分析。而较看孟子此章。为不悖本旨。未知此说如何。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周子太极图说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通书又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既谓之各一其性。则固有分于太极之浑然矣。既谓之非诚非也。则诚与五常。亦有间矣。
真有不同者也。或说以为孟子说犬牛人之性不同。亦是只说理一边。此说果何如耶。臣滢修对曰。前章之言性。以人而言。故专言理。此章之言性。较人物而言。故兼言气。盖人物之生。固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气。而理无不同。气或不齐。则于是乎人物之禀。有偏有全。而其性亦有通塞之异也。然以人而言。则气质之禀。粹驳虽异。而本然之体。圣凡皆同。此孟子之言人性则以为无不善。言人物之性则以为不同。而前后之言。初无有不合者也。若谓孟子之言犬牛人性之不同。亦从理一边说而无关于气。则理无同异矣。人物偏全之殊。将何处见得耶。此说恐不得为定论也。 御制条问曰。五常之性。对太极浑然之体而言。则为气质之性。各指其气之理。故有五者之分焉。对气禀善恶之性而言。则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而言。故纯善无恶。说者曰。如是分析。而较看孟子此章。为不悖本旨。未知此说如何。臣滢修对曰。臣谨按周子太极图说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通书又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既谓之各一其性。则固有分于太极之浑然矣。既谓之非诚非也。则诚与五常。亦有间矣。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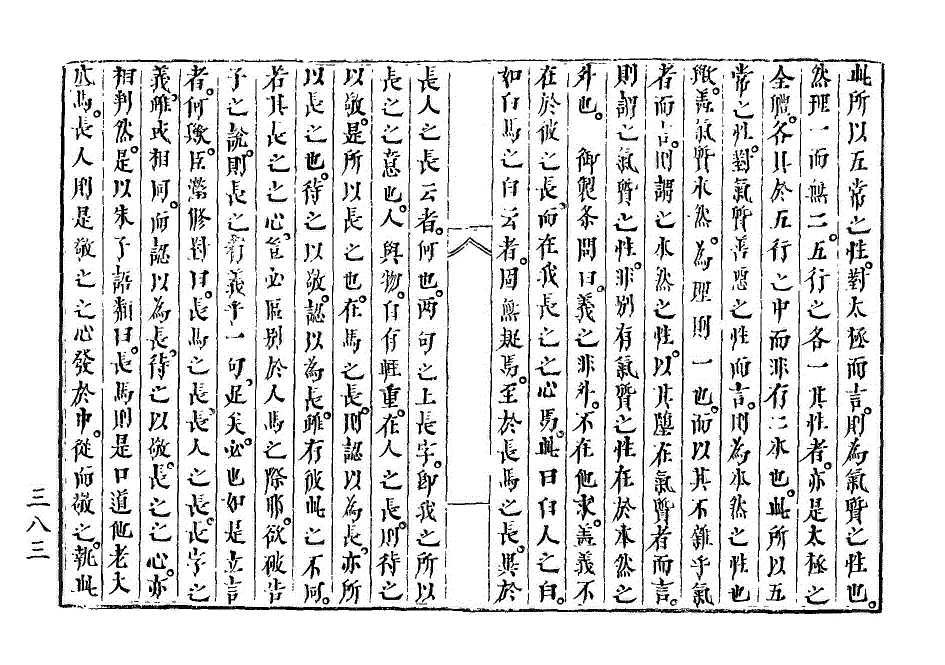 此所以五常之性。对太极而言。则为气质之性也。然理一而无二。五行之各一其性者。亦是太极之全体。各具于五行之中而非有二本也。此所以五常之性。对气质善恶之性而言。则为本然之性也欤。盖气质本然。为理则一也。而以其不杂乎气者而言。则谓之本然之性。以其堕在气质者而言。则谓之气质之性。非别有气质之性在于本然之外也。 御制条问曰。义之非外。不在他求。盖义不在于彼之长。而在我长之之心焉。此曰白人之白。如白马之白云者。固无疑焉。至于长马之长。异于长人之长云者。何也。两句之上长字。即我之所以长之之意也。人与物。自有轻重。在人之长。则待之以敬。是所以长之也。在马之长。则认以为长。亦所以长之也。待之以敬。认以为长。虽有彼此之不同。若其长之之心。岂必区别于人马之际耶。欲破告子之说。则长之者义乎一句。足矣。必也如是立言者。何欤。臣滢修对曰。长马之长。长人之长。长字之义。虽或相同。而认以为长。待之以敬。长之之心。亦相判然。是以朱子语类曰。长马则是口道他老大底马。长人则是敬之之心发于中。从而敬之。执此
此所以五常之性。对太极而言。则为气质之性也。然理一而无二。五行之各一其性者。亦是太极之全体。各具于五行之中而非有二本也。此所以五常之性。对气质善恶之性而言。则为本然之性也欤。盖气质本然。为理则一也。而以其不杂乎气者而言。则谓之本然之性。以其堕在气质者而言。则谓之气质之性。非别有气质之性在于本然之外也。 御制条问曰。义之非外。不在他求。盖义不在于彼之长。而在我长之之心焉。此曰白人之白。如白马之白云者。固无疑焉。至于长马之长。异于长人之长云者。何也。两句之上长字。即我之所以长之之意也。人与物。自有轻重。在人之长。则待之以敬。是所以长之也。在马之长。则认以为长。亦所以长之也。待之以敬。认以为长。虽有彼此之不同。若其长之之心。岂必区别于人马之际耶。欲破告子之说。则长之者义乎一句。足矣。必也如是立言者。何欤。臣滢修对曰。长马之长。长人之长。长字之义。虽或相同。而认以为长。待之以敬。长之之心。亦相判然。是以朱子语类曰。长马则是口道他老大底马。长人则是敬之之心发于中。从而敬之。执此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4H 页
 观之。则长马长人之长。虽若无区别。而其所以有区别者。正在于认以为长敬以待之之分矣。告子之言。既以白喻长。则孟子之对之也。不得不以白马之白。白人之白。虽可同谓之白。而长马之长。长人之长。不可同以为长之意以破之。而其要意大指。则固专在于长之者义乎一句也。 御制条问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朱子斥之曰。此近世苏氏胡氏之说也。尝按东坡说。以为自尧舜以来。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尝分善恶言也。又按五峰说。以为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又按文定说。语意略相似。而至以为才说性时。须与恶对。后世明儒阳明子又宗此三说而转益猖狂。似此议论。诳惑后学。流弊滔滔不息。可胜叹哉。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则是何异于铜铁金银之搅作一器耶。然程子之言。则以为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以是龟山馀派。浸浸入于苏胡之说。程朱立言之同异。亦可详言耶。未发以前。亦尝有所谓善恶耶。然则告子说中性无善无不善之句。属之人生而静以上。谓以善恶未判时节。则果何如耶。第一
观之。则长马长人之长。虽若无区别。而其所以有区别者。正在于认以为长敬以待之之分矣。告子之言。既以白喻长。则孟子之对之也。不得不以白马之白。白人之白。虽可同谓之白。而长马之长。长人之长。不可同以为长之意以破之。而其要意大指。则固专在于长之者义乎一句也。 御制条问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朱子斥之曰。此近世苏氏胡氏之说也。尝按东坡说。以为自尧舜以来。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尝分善恶言也。又按五峰说。以为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又按文定说。语意略相似。而至以为才说性时。须与恶对。后世明儒阳明子又宗此三说而转益猖狂。似此议论。诳惑后学。流弊滔滔不息。可胜叹哉。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则是何异于铜铁金银之搅作一器耶。然程子之言。则以为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以是龟山馀派。浸浸入于苏胡之说。程朱立言之同异。亦可详言耶。未发以前。亦尝有所谓善恶耶。然则告子说中性无善无不善之句。属之人生而静以上。谓以善恶未判时节。则果何如耶。第一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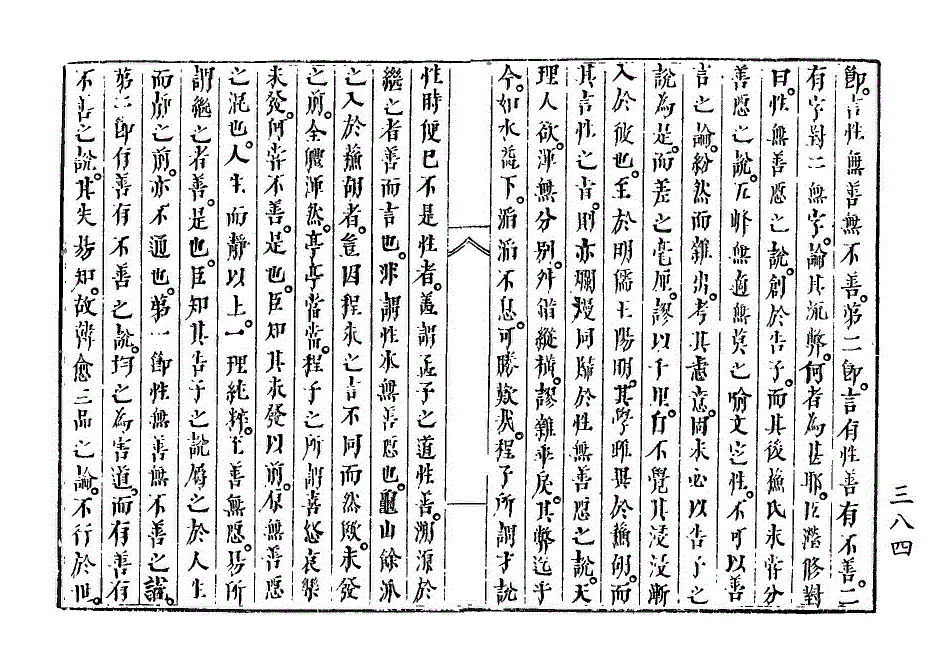 节。言性无善无不善。第二节。言有性善有不善。二有字对二无字。论其流弊。何者为甚耶。臣滢修对曰。性无善恶之说。创于告子。而其后苏氏未尝分善恶之说。五峰无适无莫之喻文定性。不可以善言之论。纷然而杂出。考其志意。固未必以告子之说为是。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不觉其浸浸渐入于彼也。至于明儒王阳明。其学虽异于苏胡。而其言性之旨。则亦烂熳同归于性无善恶之说。天理人欲。浑无分别。舛错纵横。谬杂乖戾。其弊迄乎今。如水益下。滔滔不息。可胜叹哉。程子所谓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盖谓孟子之道性善。溯源于继之者善而言也。非谓性本无善恶也。龟山馀派之入于苏胡者。岂因程朱之言不同而然欤。未发之前。全体浑然。亭亭当当。程子之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是也。臣知其未发以前。原无善恶之混也。人生而静以上。一理纯粹。至善无恶。易所谓继之者善。是也。臣知其告子之说属之于人生而静之前。亦不通也。第一节性无善无不善之说。第二节有善有不善之说。均之为害道。而有善有不善之说。其失易知。故韩愈三品之论。不行于世。
节。言性无善无不善。第二节。言有性善有不善。二有字对二无字。论其流弊。何者为甚耶。臣滢修对曰。性无善恶之说。创于告子。而其后苏氏未尝分善恶之说。五峰无适无莫之喻文定性。不可以善言之论。纷然而杂出。考其志意。固未必以告子之说为是。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不觉其浸浸渐入于彼也。至于明儒王阳明。其学虽异于苏胡。而其言性之旨。则亦烂熳同归于性无善恶之说。天理人欲。浑无分别。舛错纵横。谬杂乖戾。其弊迄乎今。如水益下。滔滔不息。可胜叹哉。程子所谓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盖谓孟子之道性善。溯源于继之者善而言也。非谓性本无善恶也。龟山馀派之入于苏胡者。岂因程朱之言不同而然欤。未发之前。全体浑然。亭亭当当。程子之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是也。臣知其未发以前。原无善恶之混也。人生而静以上。一理纯粹。至善无恶。易所谓继之者善。是也。臣知其告子之说属之于人生而静之前。亦不通也。第一节性无善无不善之说。第二节有善有不善之说。均之为害道。而有善有不善之说。其失易知。故韩愈三品之论。不行于世。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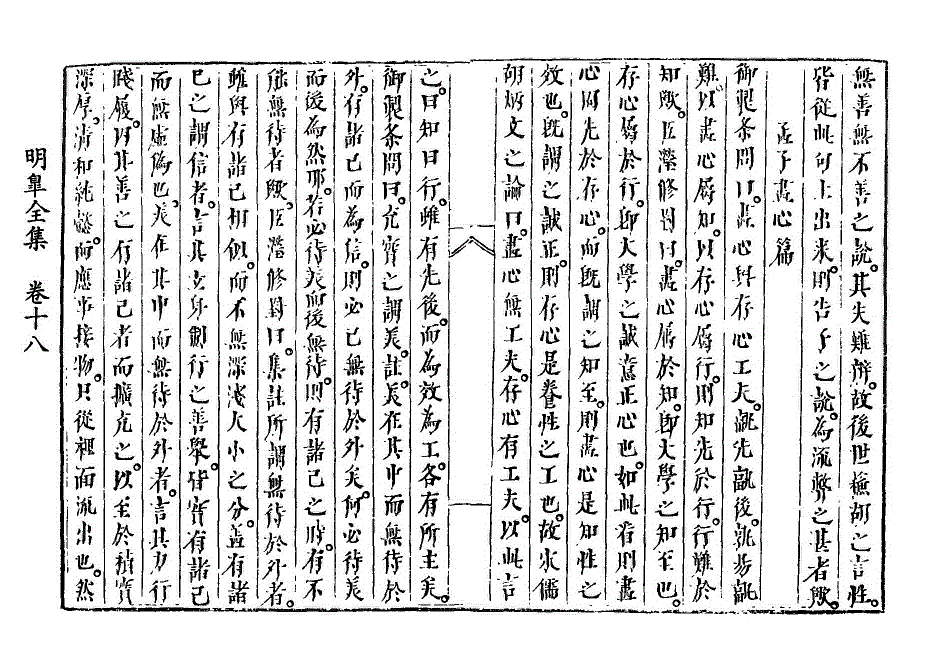 无善无不善之说。其失难辨。故后世苏胡之言性。皆从此句上出来。则告子之说。为流弊之甚者欤。
无善无不善之说。其失难辨。故后世苏胡之言性。皆从此句上出来。则告子之说。为流弊之甚者欤。孟子尽心篇
御制条问曰。尽心与存心工夫。孰先孰后。孰易孰难。以尽心属知。以存心属行。则知先于行。行难于知欤。臣滢修对曰。尽心属于知。即大学之知至也。存心属于行。即大学之诚意正心也。如此看则尽心固先于存心。而既谓之知至。则尽心是知性之效也。既谓之诚正。则存心是养性之工也。故宋儒胡炳文之论曰。尽心无工夫。存心有工夫。以此言之。曰知曰行。虽有先后。而为效为工。各有所主矣。御制条问曰。充实之谓美。注。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有诸己而为信。则必已无待于外矣。何必待美而后为然耶。若必待美而后无待。则有诸己之时。有不能无待者欤。臣滢修对曰。集注所谓无待于外者。虽与有诸己相似。而不无深浅大小之分。盖有诸己之谓信者。言其立身制行之善举。皆实有诸己而无虚伪也。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者。言其力行践履。因其善之有诸己者而扩充之。以至于积实深厚。清和纯懿。而应事接物。只从里面流出也。然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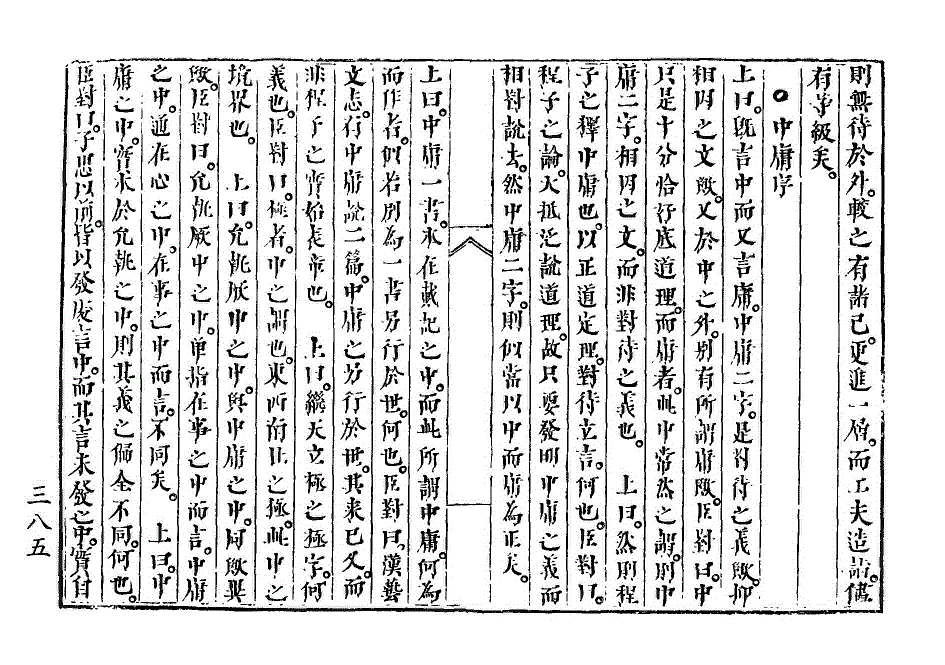 则无待于外。较之有诸己。更进一层。而工夫造诣。尽有等级矣。
则无待于外。较之有诸己。更进一层。而工夫造诣。尽有等级矣。中庸序
上曰。既言中而又言庸。中庸二字。是对待之义欤。抑相因之文欤。又于中之外。别有所谓庸欤。臣对曰。中只是十分恰好底道理。而庸者。此中常然之谓。则中庸二字。相因之文。而非对待之义也。 上曰。然则程子之释中庸也。以正道定理。对待立言。何也。臣对曰。程子之论。大抵泛说道理。故只要发明中庸之义而相对说去。然中庸二字。则似当以中而庸为正矣。 上曰。中庸一书。本在戴记之中。而此所谓中庸。何为而作者。似若别为一书另行于世。何也。臣对曰。汉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中庸之另行于世。其来已久。而非程子之实始表章也。 上曰。继天立极之极字。何义也。臣对曰。极者。中之谓也。东西南北之极。此中之境界也。 上曰。允执厥中之中。与中庸之中。同欤异欤。臣对曰。允执厥中之中。单指在事之中而言。中庸之中。通在心之中。在事之中而言。不同矣。 上曰。中庸之中。实本于允执之中。则其义之偏全不同。何也。臣对曰。子思以前。皆以发处言中。而其言未发之中。实自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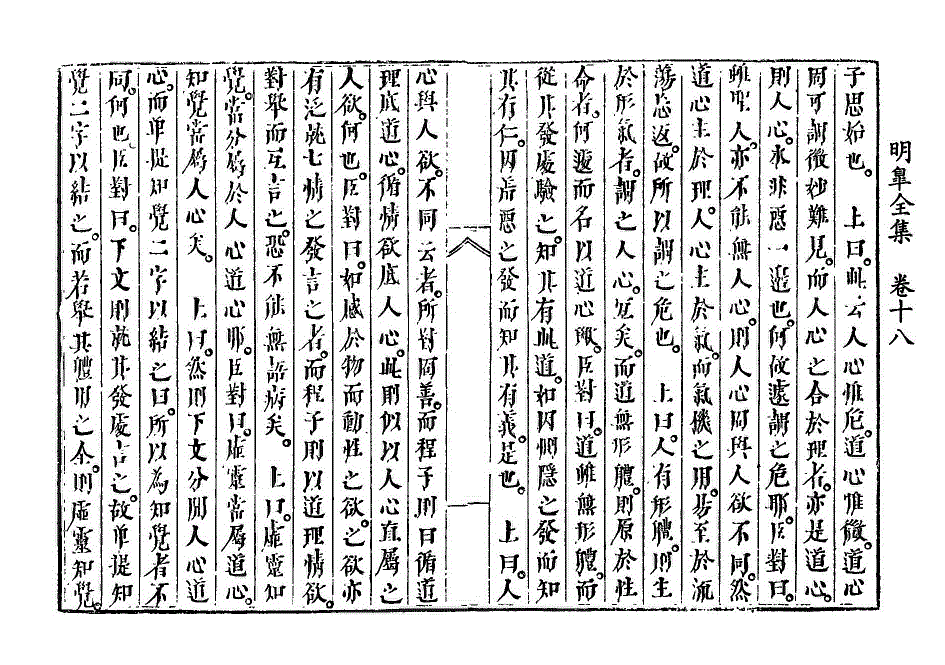 子思始也。 上曰。此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可谓微妙难见。而人心之合于理者。亦是道心。则人心。本非恶一边也。何故遽谓之危耶。臣对曰。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则人心固与人欲不同。然道心主于理。人心主于气。而气机之用。易至于流荡忘返。故所以谓之危也。 上曰。人有形体。则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宜矣。而道无形体。则原于性命者。何遽而名以道心欤。臣对曰。道虽无形体。而从其发处验之。知其有此道。如因恻隐之发而知其有仁。因羞恶之发而知其有义。是也。 上曰。人心与人欲。不同云者。所对固善。而程子则曰循道理底道心。循情欲底人心。此则似以人心直属之人欲。何也。臣对曰。如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之欲亦有泛就七情之发言之者。而程子则以道理情欲。对举而互言之。恐不能无语病矣。 上曰。虚灵知觉。当分属于人心道心耶。臣对曰。虚灵当属道心。知觉当属人心矣。 上曰。然则下文分开人心道心。而单提知觉二字以结之曰。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何也。臣对曰。下文则就其发处言之。故单提知觉二字以结之。而若举其体用之全。则虚灵知觉。
子思始也。 上曰。此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可谓微妙难见。而人心之合于理者。亦是道心。则人心。本非恶一边也。何故遽谓之危耶。臣对曰。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则人心固与人欲不同。然道心主于理。人心主于气。而气机之用。易至于流荡忘返。故所以谓之危也。 上曰。人有形体。则生于形气者。谓之人心。宜矣。而道无形体。则原于性命者。何遽而名以道心欤。臣对曰。道虽无形体。而从其发处验之。知其有此道。如因恻隐之发而知其有仁。因羞恶之发而知其有义。是也。 上曰。人心与人欲。不同云者。所对固善。而程子则曰循道理底道心。循情欲底人心。此则似以人心直属之人欲。何也。臣对曰。如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之欲亦有泛就七情之发言之者。而程子则以道理情欲。对举而互言之。恐不能无语病矣。 上曰。虚灵知觉。当分属于人心道心耶。臣对曰。虚灵当属道心。知觉当属人心矣。 上曰。然则下文分开人心道心。而单提知觉二字以结之曰。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何也。臣对曰。下文则就其发处言之。故单提知觉二字以结之。而若举其体用之全。则虚灵知觉。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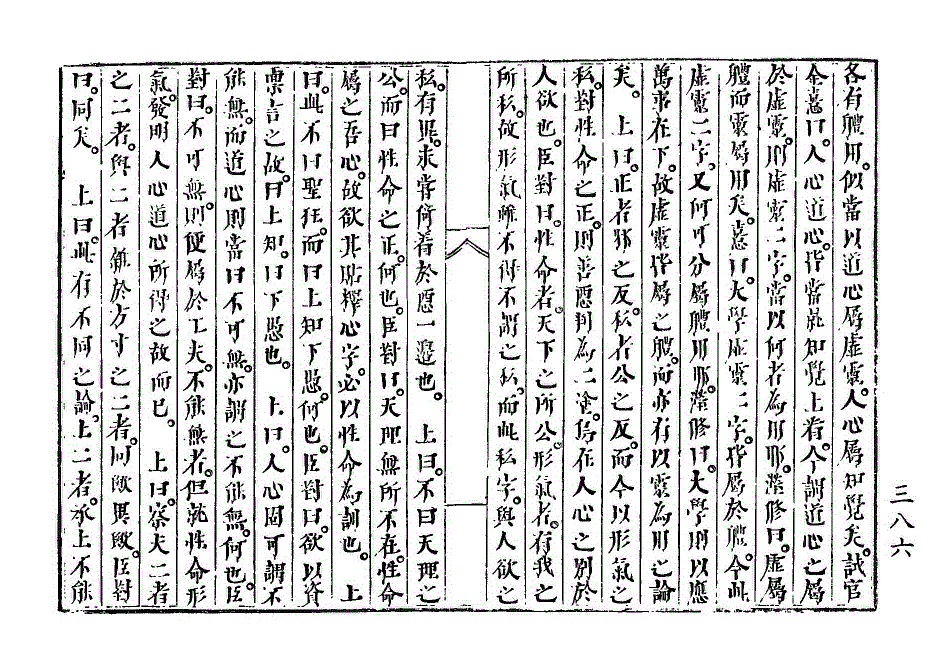 各有体用。似当以道心属虚灵。人心属知觉矣。试官金憙曰。人心道心。皆当就知觉上看。今谓道心之属于虚灵。则虚灵二字。当以何者为用耶。滢修曰。虚属体而灵属用矣。憙曰。大学虚灵二字。皆属于体。今此虚灵二字。又何可分属体用耶。滢修曰。大学则以应万事在下。故虚灵皆属之体。而亦有以灵为用之论矣。 上曰。正者邪之反。私者公之反。而今以形气之私。对性命之正。则善恶判为二涂。乌在人心之别于人欲也。臣对曰。性命者。天下之所公。形气者。有我之所私。故形气虽不得不谓之私。而此私字。与人欲之私。有异。未尝倚着于恶一边也。 上曰。不曰天理之公。而曰性命之正。何也。臣对曰。天理无所不在。性命属之吾心。故欲其贴释心字。必以性命为训也。 上曰。此不曰圣狂。而曰上知下愚。何也。臣对曰。欲以资禀言之故。曰上知。曰下愚也。 上曰。人心固可谓不能无。而道心则当曰不可无。亦谓之不能无。何也。臣对曰。不可无。则便属于工夫。不能无者。但就性命形气。发明人心道心所得之故而已。 上曰。察夫二者之二者。与二者杂于方寸之二者。同欤异欤。臣对曰。同矣。 上曰。此有不同之论。上二者。承上不能
各有体用。似当以道心属虚灵。人心属知觉矣。试官金憙曰。人心道心。皆当就知觉上看。今谓道心之属于虚灵。则虚灵二字。当以何者为用耶。滢修曰。虚属体而灵属用矣。憙曰。大学虚灵二字。皆属于体。今此虚灵二字。又何可分属体用耶。滢修曰。大学则以应万事在下。故虚灵皆属之体。而亦有以灵为用之论矣。 上曰。正者邪之反。私者公之反。而今以形气之私。对性命之正。则善恶判为二涂。乌在人心之别于人欲也。臣对曰。性命者。天下之所公。形气者。有我之所私。故形气虽不得不谓之私。而此私字。与人欲之私。有异。未尝倚着于恶一边也。 上曰。不曰天理之公。而曰性命之正。何也。臣对曰。天理无所不在。性命属之吾心。故欲其贴释心字。必以性命为训也。 上曰。此不曰圣狂。而曰上知下愚。何也。臣对曰。欲以资禀言之故。曰上知。曰下愚也。 上曰。人心固可谓不能无。而道心则当曰不可无。亦谓之不能无。何也。臣对曰。不可无。则便属于工夫。不能无者。但就性命形气。发明人心道心所得之故而已。 上曰。察夫二者之二者。与二者杂于方寸之二者。同欤异欤。臣对曰。同矣。 上曰。此有不同之论。上二者。承上不能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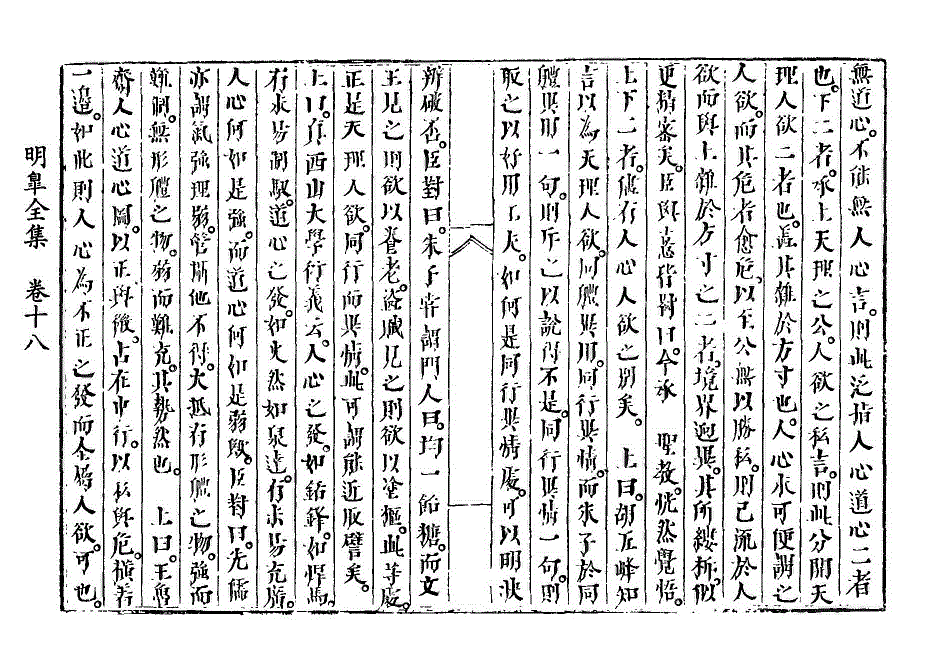 无道心。不能无人心言。则此泛指人心道心二者也。下二者。承上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言。则此分开天理人欲二者也。盖其杂于方寸也。人心未可便谓之人欲。而其危者愈危。以至公无以胜私。则已流于人欲而与上杂于方寸之二者。境界迥异。其所缕析。似更精密矣。臣与憙皆对曰。今承 圣教。恍然觉悟。上下二者。尽有人心人欲之别矣。 上曰。胡五峰知言以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而朱子于同体异用一句。则斥之以说得不是。同行异情一句。则取之以好用工夫。如何是同行异情处。可以明快辨破否。臣对曰。朱子尝谓门人曰。均一饴糖。而文王见之则欲以养老。盗贼见之则欲以涂枢。此等处。正是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此可谓能近取譬矣。 上曰。真西山大学衍义云。人心之发。如铦锋。如悍马。有未易制驭。道心之发。如火然如泉达。有未易充广。人心何如是强。而道心何如是弱欤。臣对曰。先儒亦谓气强理弱。管摄他不得。大抵有形体之物。强而难制。无形体之物。弱而难充。其势然也。 上曰。王鲁斋人心道心图。以正与微。占在中行。以私与危。横着一边。如此则人心为不正之发而全属人欲。可也。
无道心。不能无人心言。则此泛指人心道心二者也。下二者。承上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言。则此分开天理人欲二者也。盖其杂于方寸也。人心未可便谓之人欲。而其危者愈危。以至公无以胜私。则已流于人欲而与上杂于方寸之二者。境界迥异。其所缕析。似更精密矣。臣与憙皆对曰。今承 圣教。恍然觉悟。上下二者。尽有人心人欲之别矣。 上曰。胡五峰知言以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而朱子于同体异用一句。则斥之以说得不是。同行异情一句。则取之以好用工夫。如何是同行异情处。可以明快辨破否。臣对曰。朱子尝谓门人曰。均一饴糖。而文王见之则欲以养老。盗贼见之则欲以涂枢。此等处。正是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此可谓能近取譬矣。 上曰。真西山大学衍义云。人心之发。如铦锋。如悍马。有未易制驭。道心之发。如火然如泉达。有未易充广。人心何如是强。而道心何如是弱欤。臣对曰。先儒亦谓气强理弱。管摄他不得。大抵有形体之物。强而难制。无形体之物。弱而难充。其势然也。 上曰。王鲁斋人心道心图。以正与微。占在中行。以私与危。横着一边。如此则人心为不正之发而全属人欲。可也。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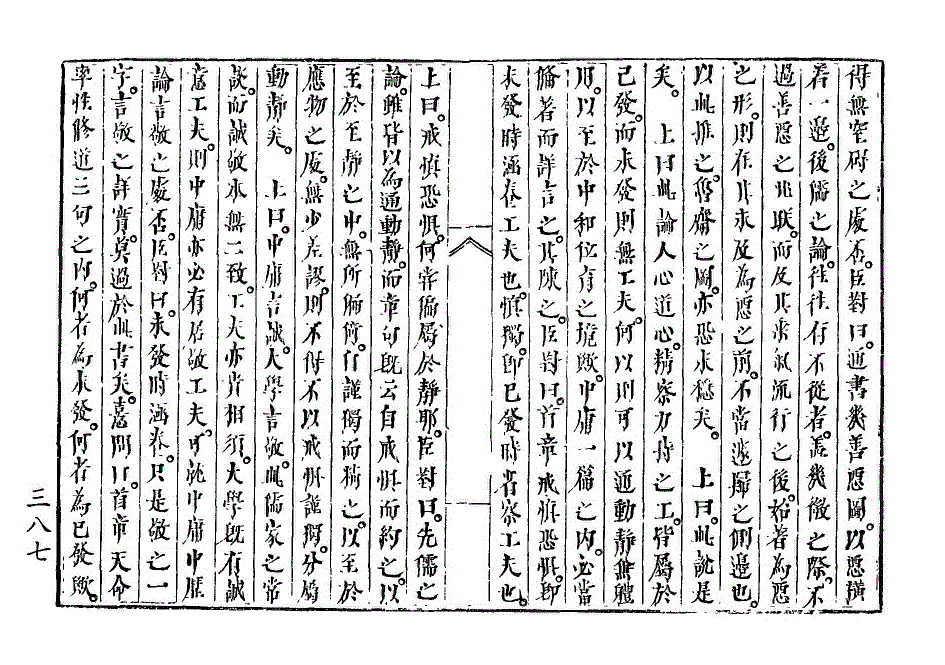 得无窒碍之处否。臣对曰。通书几善恶图。以恶横着一边。后儒之论。往往有不从者。盖几微之际。不过善恶之兆眹。而及其乘气流行之后。始著为恶之形。则在其未及为恶之前。不当邃归之侧边也。以此推之。鲁斋之图。亦恐未稳矣。 上曰。此说是矣。 上曰此论人心道心。精察力持之工。皆属于已发。而未发则无工夫。何以则可以通动静兼体用。以至于中和位育之境欤。中庸一篇之内。必当备著而详言之。其陈之。臣对曰。首章戒慎恐惧。即未发时涵养工夫也。慎独。即已发时省察工夫也。上曰。戒慎恐惧。何尝偏属于静耶。臣对曰。先儒之论。虽皆以为通动静。而章句既云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则不得不以戒州谨独。分属动静矣。 上曰。中庸言诚。大学言敬。此儒家之常谈。而诚敬本无二致。工夫亦贵相须。大学既有诚意工夫。则中庸亦必有居敬工夫。可就中庸中历论言敬之处否。臣对曰。未发时涵养。只是敬之一字。言敬之详实。莫过于此书矣。憙问曰。首章天命率性修道三句之内。何者为未发。何者为已发欤。
得无窒碍之处否。臣对曰。通书几善恶图。以恶横着一边。后儒之论。往往有不从者。盖几微之际。不过善恶之兆眹。而及其乘气流行之后。始著为恶之形。则在其未及为恶之前。不当邃归之侧边也。以此推之。鲁斋之图。亦恐未稳矣。 上曰。此说是矣。 上曰此论人心道心。精察力持之工。皆属于已发。而未发则无工夫。何以则可以通动静兼体用。以至于中和位育之境欤。中庸一篇之内。必当备著而详言之。其陈之。臣对曰。首章戒慎恐惧。即未发时涵养工夫也。慎独。即已发时省察工夫也。上曰。戒慎恐惧。何尝偏属于静耶。臣对曰。先儒之论。虽皆以为通动静。而章句既云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则不得不以戒州谨独。分属动静矣。 上曰。中庸言诚。大学言敬。此儒家之常谈。而诚敬本无二致。工夫亦贵相须。大学既有诚意工夫。则中庸亦必有居敬工夫。可就中庸中历论言敬之处否。臣对曰。未发时涵养。只是敬之一字。言敬之详实。莫过于此书矣。憙问曰。首章天命率性修道三句之内。何者为未发。何者为已发欤。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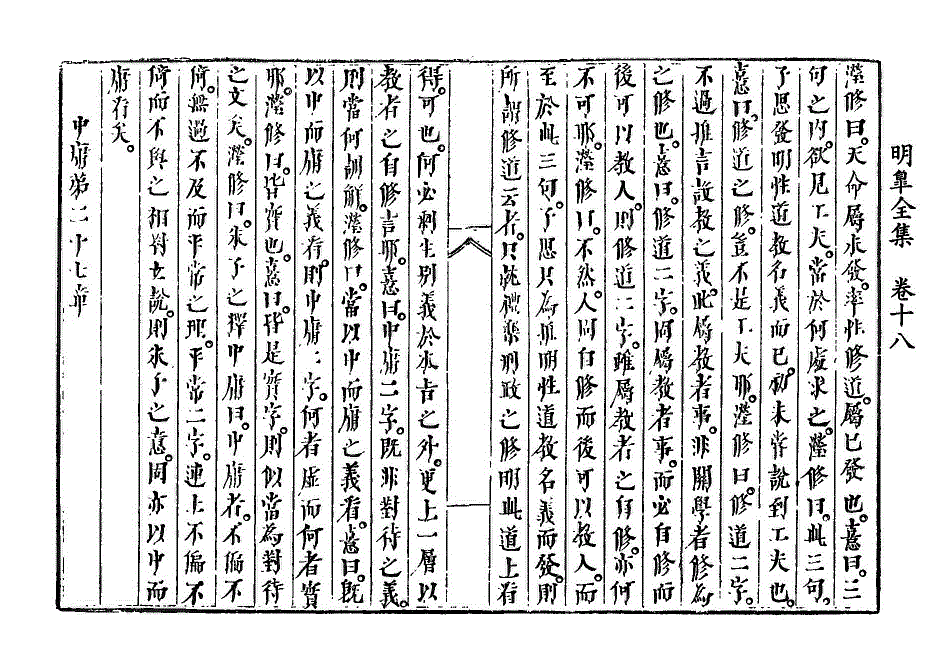 滢修曰。天命属未发。率性修道。属已发也。憙曰。三句之内。欲见工夫。当于何处求之。滢修曰。此三句。子思发明性道教名义而已。初未尝说到工夫也。憙曰。修道之修。岂不是工夫耶。滢修曰。修道二字。不过推言设教之义。此属教者事。非关学者修为之修也。憙曰。修道二字。固属教者事。而必自修而后可以教人。则修道二字。虽属教者之自修。亦何不可耶。滢修曰。不然。人固自修而后可以教人。而至于此三句。子思只为推明性道教名义而发。则所谓修道云者。只就礼乐刑政之修明此道上看得。可也。何必剩生别义于本旨之外。更上一层以教者之自修言耶。憙曰。中庸二字。既非对待之义。则当何训解。滢修曰。当以中而庸之义看。憙曰。既以中而庸之义看。则中庸二字。何者虚而何者实耶。滢修曰。皆实也。憙曰。皆是实字。则似当为对待之文矣。滢修曰。朱子之释中庸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平常二字。连上不偏不倚而不与之相对立说。则朱子之意。固亦以中而庸看矣。
滢修曰。天命属未发。率性修道。属已发也。憙曰。三句之内。欲见工夫。当于何处求之。滢修曰。此三句。子思发明性道教名义而已。初未尝说到工夫也。憙曰。修道之修。岂不是工夫耶。滢修曰。修道二字。不过推言设教之义。此属教者事。非关学者修为之修也。憙曰。修道二字。固属教者事。而必自修而后可以教人。则修道二字。虽属教者之自修。亦何不可耶。滢修曰。不然。人固自修而后可以教人。而至于此三句。子思只为推明性道教名义而发。则所谓修道云者。只就礼乐刑政之修明此道上看得。可也。何必剩生别义于本旨之外。更上一层以教者之自修言耶。憙曰。中庸二字。既非对待之义。则当何训解。滢修曰。当以中而庸之义看。憙曰。既以中而庸之义看。则中庸二字。何者虚而何者实耶。滢修曰。皆实也。憙曰。皆是实字。则似当为对待之文矣。滢修曰。朱子之释中庸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平常二字。连上不偏不倚而不与之相对立说。则朱子之意。固亦以中而庸看矣。中庸第二十七章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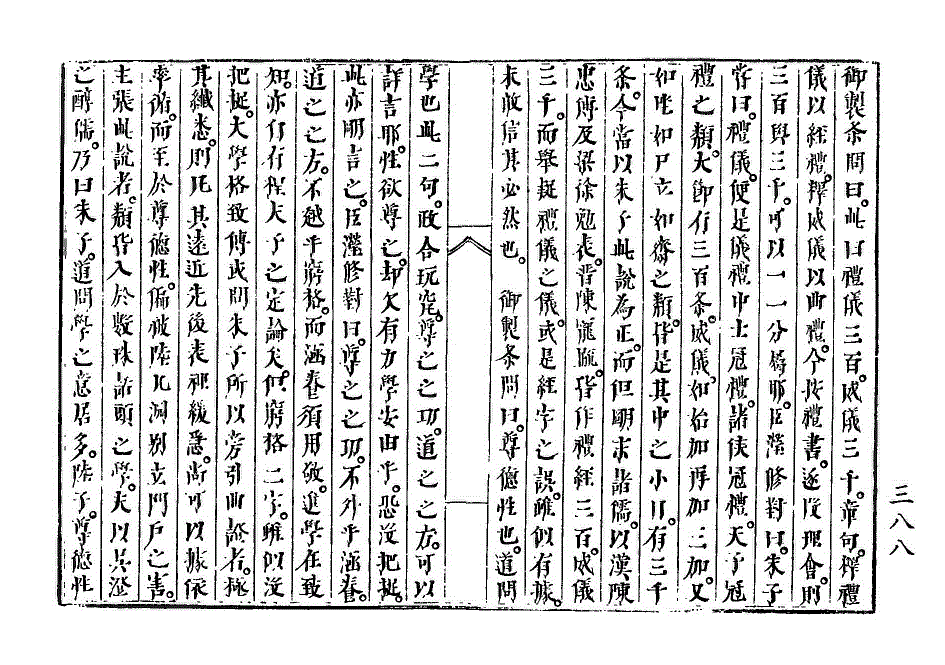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此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章句。释礼仪以经礼。释威仪以曲礼。今按礼书。逐段理会。则三百与三千。可以一一分属耶。臣滢修对曰。朱子尝曰。礼仪。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天子冠礼之类。大节有三百条。威仪。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斋之类。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条。今当以朱子此说为正。而但明末诸儒。以汉陈忠传及梁徐勉表。晋陈宠疏。皆作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举疑礼仪之仪。或是经字之误。虽似有据。未敢信其必然也。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也。道问学也此二句。政合玩究。尊之之功。道之之方。可以详言耶。性欲尊之。却欠有力学安由乎。恐没把捉。此亦明言之。臣滢修对曰。尊之之功。不外乎涵养。道之之方。不越乎穷格。而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亦自有程夫子之定论矣。但穷格二字。虽似没把捉。大学格致传或问朱子所以旁引曲證者。极其纤悉。则凡其远近先后表里缓急。尚可以据依率循。而至于尊德性。偏被陆九渊别立门户之害。主张此说者。类皆入于数珠话头之学。夫以吴澄之醇儒。乃曰朱子。道问学之意居多。陆子。尊德性
御制条问曰。此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章句。释礼仪以经礼。释威仪以曲礼。今按礼书。逐段理会。则三百与三千。可以一一分属耶。臣滢修对曰。朱子尝曰。礼仪。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天子冠礼之类。大节有三百条。威仪。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斋之类。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条。今当以朱子此说为正。而但明末诸儒。以汉陈忠传及梁徐勉表。晋陈宠疏。皆作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举疑礼仪之仪。或是经字之误。虽似有据。未敢信其必然也。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也。道问学也此二句。政合玩究。尊之之功。道之之方。可以详言耶。性欲尊之。却欠有力学安由乎。恐没把捉。此亦明言之。臣滢修对曰。尊之之功。不外乎涵养。道之之方。不越乎穷格。而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亦自有程夫子之定论矣。但穷格二字。虽似没把捉。大学格致传或问朱子所以旁引曲證者。极其纤悉。则凡其远近先后表里缓急。尚可以据依率循。而至于尊德性。偏被陆九渊别立门户之害。主张此说者。类皆入于数珠话头之学。夫以吴澄之醇儒。乃曰朱子。道问学之意居多。陆子。尊德性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9H 页
 之意居多。则况其下者乎。于是乎调停朱陆之论。前唱后喁。程敏政之道一编。王守仁之晚年定论。李绂之晚年全论。至于今莫可辨诘。夫朱子之教。固以穷格为务。而每谓穷格之前。不可不涵养本源。则何尝阙略于尊德性之工。陆子之所谓尊之者。又不免专就虚静。悬空摸索。则曾以是谓之涵养。可乎。盖此尊之一字。即勿着力勿放过之意也。与大学之顾諟。颜子之服膺。孟子之勿忘勿助。同一旨义。而程子之主一无适。谢显道之常惺惺法。尹彦明之其心收敛。皆所以指示工夫之境界也。何必费力纷纠。反累其湛然之本体然后方谓之尊德性哉。 御制条问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四段。属于尊德性。而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四段。属于道问学。章句或问。以此言之详矣。但温故。似属道问学。而今必属于尊德性。何也。崇礼。似属尊德性。而今必属于道问学。何也。至于道中庸之属于道问学。尤不胜愤悱。盖知行之无过不及。道体之至大至小。莫不包在于中庸二字之中。则此二字。恐不当偏属于知。谓之以小。而章句所谓致知之属。道中庸。居其一焉。或问所谓一句之
之意居多。则况其下者乎。于是乎调停朱陆之论。前唱后喁。程敏政之道一编。王守仁之晚年定论。李绂之晚年全论。至于今莫可辨诘。夫朱子之教。固以穷格为务。而每谓穷格之前。不可不涵养本源。则何尝阙略于尊德性之工。陆子之所谓尊之者。又不免专就虚静。悬空摸索。则曾以是谓之涵养。可乎。盖此尊之一字。即勿着力勿放过之意也。与大学之顾諟。颜子之服膺。孟子之勿忘勿助。同一旨义。而程子之主一无适。谢显道之常惺惺法。尹彦明之其心收敛。皆所以指示工夫之境界也。何必费力纷纠。反累其湛然之本体然后方谓之尊德性哉。 御制条问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四段。属于尊德性。而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四段。属于道问学。章句或问。以此言之详矣。但温故。似属道问学。而今必属于尊德性。何也。崇礼。似属尊德性。而今必属于道问学。何也。至于道中庸之属于道问学。尤不胜愤悱。盖知行之无过不及。道体之至大至小。莫不包在于中庸二字之中。则此二字。恐不当偏属于知。谓之以小。而章句所谓致知之属。道中庸。居其一焉。或问所谓一句之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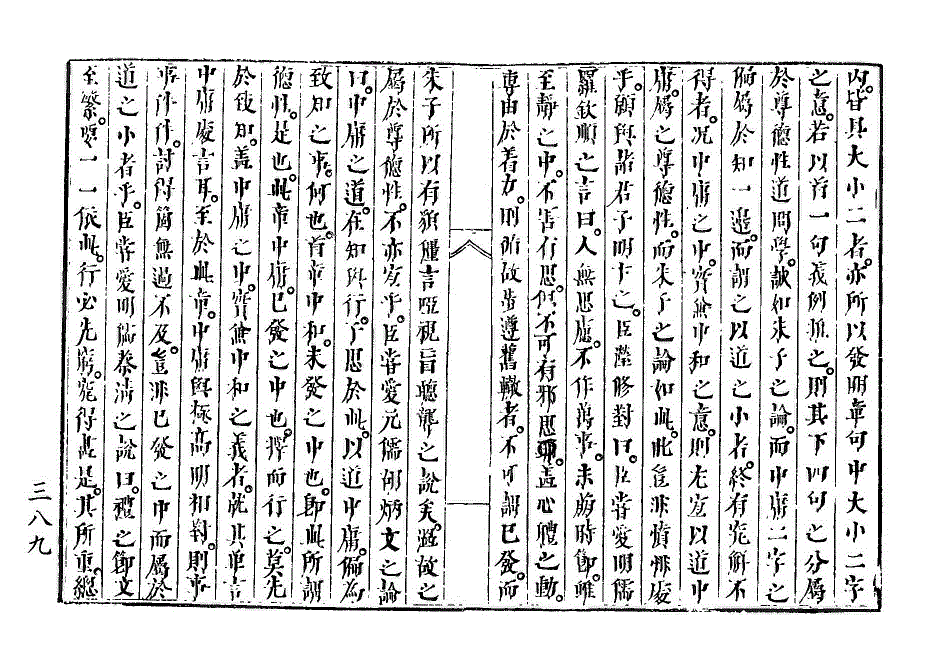 内。皆具大小二者。亦所以发明章句中大小二字之意。若以首一句义例推之。则其下四句之分属于尊德性道问学。诚如朱子之论。而中庸二字之偏属于知一边。而谓之以道之小者。终有究解不得者。况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尤宜以道中庸。属之尊德性。而朱子之论如此。此岂非愤悱处乎。愿与诸君子明卞之。臣滢修对曰。臣尝爱明儒罗钦顺之言曰。人无思虑。不作万事。未萌时节。虽至静之中。不害有思。但不可有邪思。盖心体之动。专由于着力。则循故步遵旧辙者。不可谓已发。而朱子所以有貌僵言哑视盲听聋之说矣。温故之属于尊德性。不亦宜乎。臣尝爱元儒胡炳文之论曰。中庸之道。在知与行。子思于此。以道中庸。偏为致知之事。何也。首章中和。未发之中也。即此所谓德性。是也。此章中庸。已发之中也。择而行之。莫先于致知。盖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者。就其单言中庸处言耳。至于此章。中庸与极高明相对。则事事件件。讨得个无过不及。岂非已发之中而属于道之小者乎。臣尝爱明儒蔡清之说曰。礼之节文至繁。要一一依此。行必先穷。究得尽是。其所重。总
内。皆具大小二者。亦所以发明章句中大小二字之意。若以首一句义例推之。则其下四句之分属于尊德性道问学。诚如朱子之论。而中庸二字之偏属于知一边。而谓之以道之小者。终有究解不得者。况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尤宜以道中庸。属之尊德性。而朱子之论如此。此岂非愤悱处乎。愿与诸君子明卞之。臣滢修对曰。臣尝爱明儒罗钦顺之言曰。人无思虑。不作万事。未萌时节。虽至静之中。不害有思。但不可有邪思。盖心体之动。专由于着力。则循故步遵旧辙者。不可谓已发。而朱子所以有貌僵言哑视盲听聋之说矣。温故之属于尊德性。不亦宜乎。臣尝爱元儒胡炳文之论曰。中庸之道。在知与行。子思于此。以道中庸。偏为致知之事。何也。首章中和。未发之中也。即此所谓德性。是也。此章中庸。已发之中也。择而行之。莫先于致知。盖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者。就其单言中庸处言耳。至于此章。中庸与极高明相对。则事事件件。讨得个无过不及。岂非已发之中而属于道之小者乎。臣尝爱明儒蔡清之说曰。礼之节文至繁。要一一依此。行必先穷。究得尽是。其所重。总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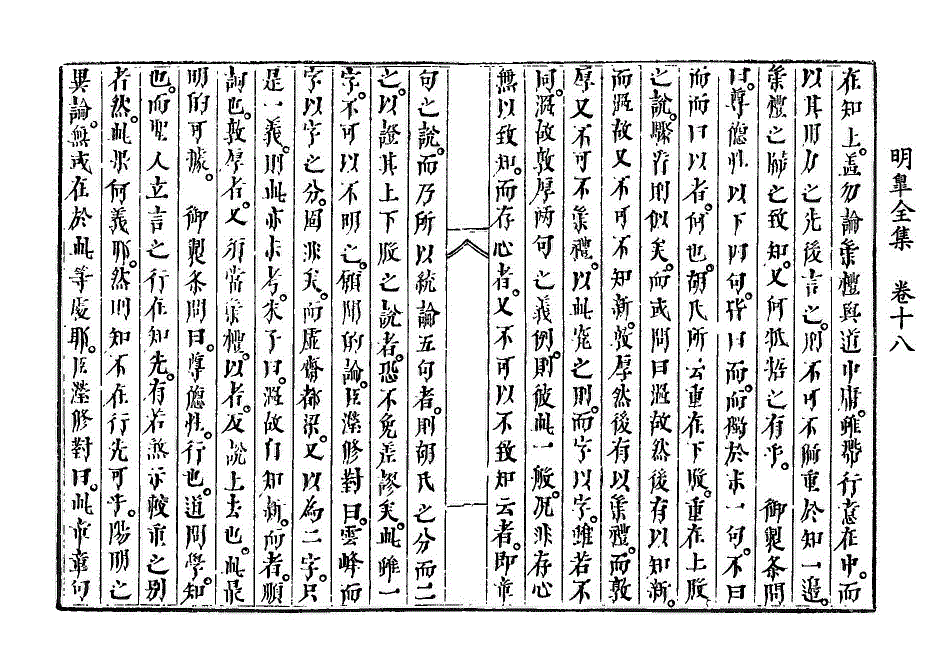 在知上。盖勿论崇礼与道中庸。虽带行意在中。而以其用力之先后言之。则不可不偏重于知一边。崇礼之归之致知。又何牴牾之有乎。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以下内句。皆曰而。而独于末一句。不曰而而曰以者。何也。胡氏所云重在下股。重在上股之说。骤看则似矣。而或问曰温故然后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后有以崇礼。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礼。以此究之则。而字以字。虽若不同。温故敦厚两句之义例。则彼此一般。况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云者。即章句之说。而乃所以统论五句者。则胡氏之分而二之。以證其上下股之说者。恐不免差谬矣。此虽一字。不可以不明之。愿闻的论。臣滢修对曰。云峰而字以字之分。固非矣。而虚斋都梁。又以为二字。只是一义。则此亦未考。朱子曰。温故自知新。而者。顺词也。敦厚者。又须当崇礼。以者。反说上去也。此最明的可据。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行也。道问学。知也。而圣人立言之行在知先。有若煞示较重之别者然。此果何义耶。然则知不在行先可乎。阳明之异论。无或在于此等处耶。臣滢修对曰。此章章句
在知上。盖勿论崇礼与道中庸。虽带行意在中。而以其用力之先后言之。则不可不偏重于知一边。崇礼之归之致知。又何牴牾之有乎。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以下内句。皆曰而。而独于末一句。不曰而而曰以者。何也。胡氏所云重在下股。重在上股之说。骤看则似矣。而或问曰温故然后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后有以崇礼。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礼。以此究之则。而字以字。虽若不同。温故敦厚两句之义例。则彼此一般。况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云者。即章句之说。而乃所以统论五句者。则胡氏之分而二之。以證其上下股之说者。恐不免差谬矣。此虽一字。不可以不明之。愿闻的论。臣滢修对曰。云峰而字以字之分。固非矣。而虚斋都梁。又以为二字。只是一义。则此亦未考。朱子曰。温故自知新。而者。顺词也。敦厚者。又须当崇礼。以者。反说上去也。此最明的可据。 御制条问曰。尊德性。行也。道问学。知也。而圣人立言之行在知先。有若煞示较重之别者然。此果何义耶。然则知不在行先可乎。阳明之异论。无或在于此等处耶。臣滢修对曰。此章章句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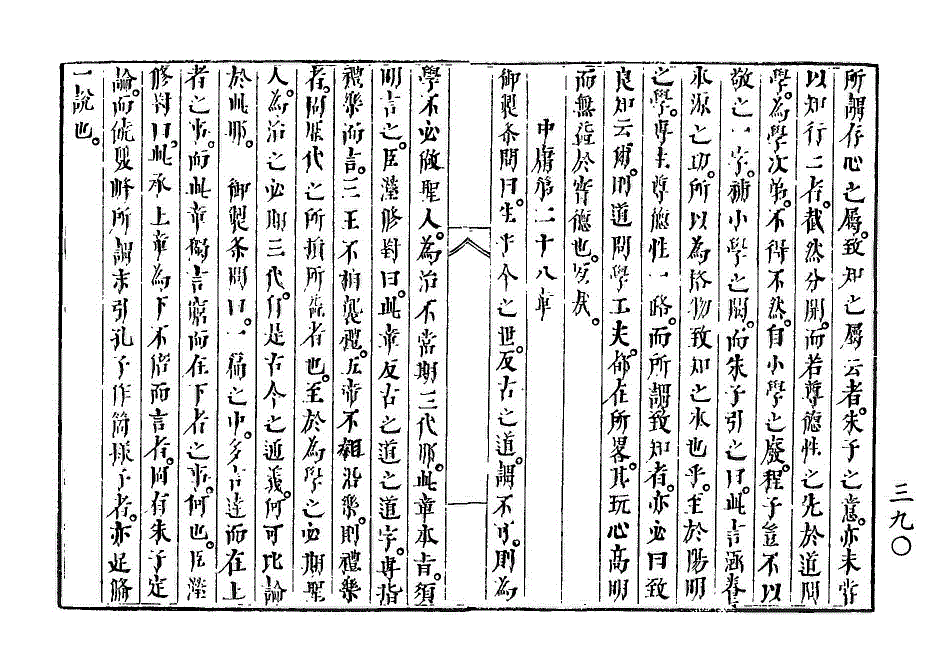 所谓存心之属。致知之属云者。朱子之意。亦未尝以知行二者。截然分开。而若尊德性之先于道问学。为学次弟。不得不然。自小学之废。程子岂不以敬之一字。补小学之阙。而朱子引之曰。此言涵养本源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也乎。至于阳明之学。专主尊德性一路。而所谓致知者。亦必曰致良知云尔。则道问学工夫。都在所略。其玩心高明而无益于实德也。宜哉。
所谓存心之属。致知之属云者。朱子之意。亦未尝以知行二者。截然分开。而若尊德性之先于道问学。为学次弟。不得不然。自小学之废。程子岂不以敬之一字。补小学之阙。而朱子引之曰。此言涵养本源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也乎。至于阳明之学。专主尊德性一路。而所谓致知者。亦必曰致良知云尔。则道问学工夫。都在所略。其玩心高明而无益于实德也。宜哉。中庸第二十八章
御制条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谓不可。则为学不必做圣人。为治不当期三代耶。此章本旨。须明言之。臣滢修对曰。此章反古之道之道字。专指礼乐而言。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则礼乐者。固历代之所损所益者也。至于为学之必期圣人。为治之必期三代。自是古今之通义。何可比论于此耶。 御制条问曰。一篇之中。多言达而在上者之事。而此章独言穷而在下者之事。何也。臣滢修对曰。此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者。固有朱子定论。而饶双峰所谓末引孔子作个㨾子者。亦足备一说也。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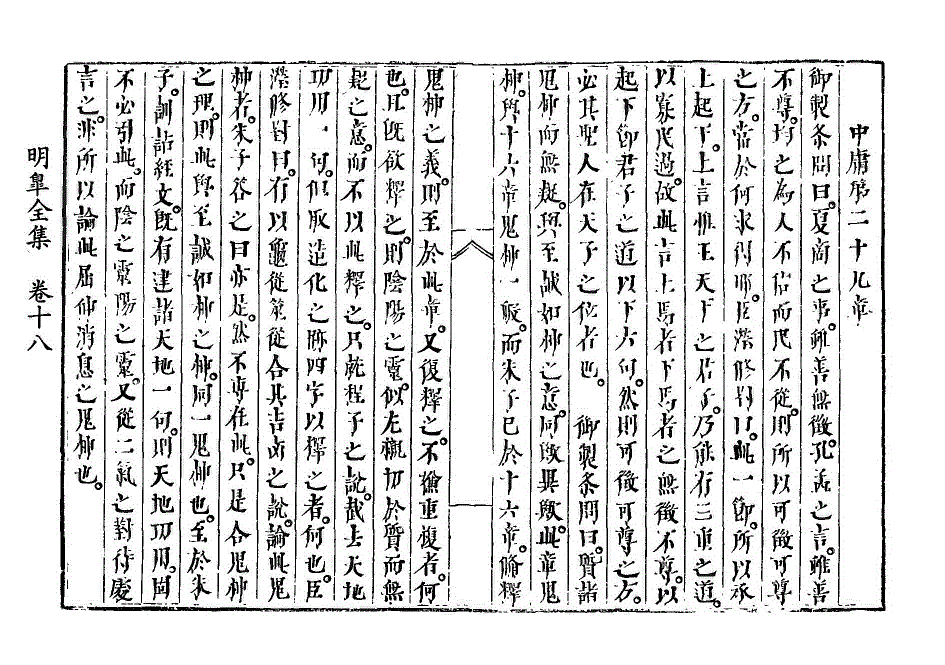 中庸第二十九章
中庸第二十九章御制条问曰。夏商之事。虽善无徵。孔孟之言。虽善不尊。均之为人不信而民不从。则所以可徵可尊之方。当于何求得耶。臣滢修对曰。此一节。所以承上起下。上言惟王天下之君子。乃能有三重之道。以寡民过。故此言上焉者下焉者之无徵不尊。以起下节君子之道以下六句。然则可徵可尊之方。必其圣人在天子之位者也。 御制条问曰。质诸鬼神而无疑。与至诚如神之意。同欤异欤。此章鬼神。与十六章鬼神一般。而朱子已于十六章。备释鬼神之义。则至于此章。又复释之。不嫌重复者。何也。且既欲释之。则阴阳之灵。似尤衬切于质而无疑之意。而不以此释之。只就程子之说。截去天地功用一句。但取造化之迹四字以释之者。何也。臣滢修对曰。有以龟从筮从合其吉凶之说。论此鬼神者。朱子答之曰亦是。然不专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则此与至诚如神之神。同一鬼神也。至于朱子。训诂经文。既有建诸天地一句。则天地功用。固不必引此。而阴之灵阳之灵。又从二气之对待处言之。非所以论此屈伸消息之鬼神也。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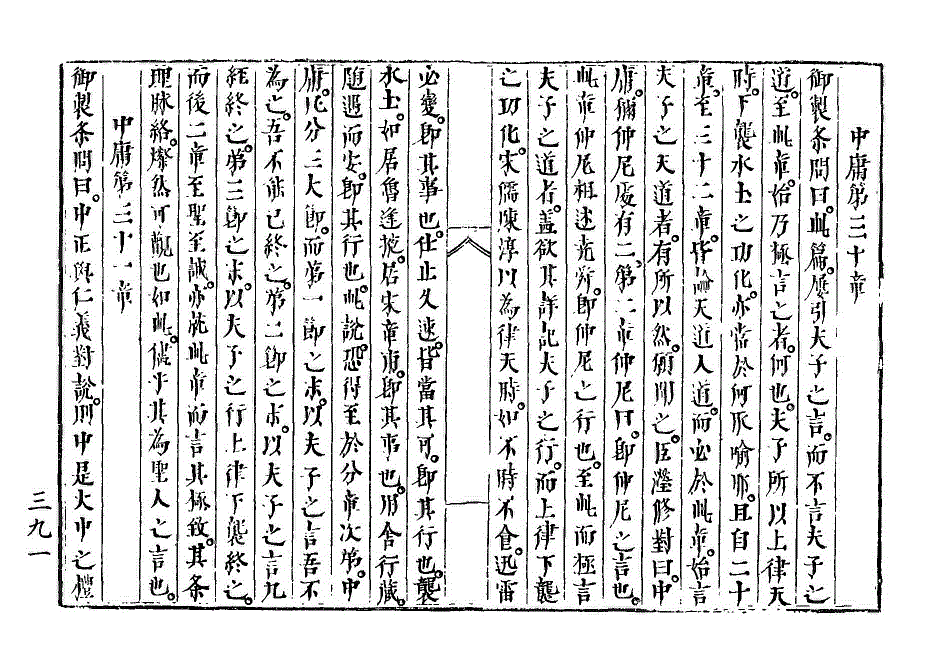 中庸第三十章
中庸第三十章御制条问曰。此篇。屡引夫子之言。而不言夫子之道。至此章。始乃极言之者。何也。夫子所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之功化。亦当于何取喻耶。且自二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论天道人道。而必于此章。始言夫子之天道者。有所以然。愿闻之。臣滢修对曰。中庸。称仲尼处有二。第二章仲尼曰。即仲尼之言也。此章仲尼祖述尧舜。即仲尼之行也。至此而极言夫子之道者。盖欲其详记夫子之行。而上律下袭之功化。宋儒陈淳以为律天时。如不时不食。迅雷必变。即其事也。仕止久速。皆当其可。即其行也。袭水土。如居鲁逢掖。居宋章甫。即其事也。用舍行藏。随遇而安。即其行也。此说。恐得至于分章次第。中庸。凡分三大节。而第一节之末。以夫子之言吾不为之。吾不能已终之。第二节之末。以夫子之言九经终之。第三节之末。以夫子之行上律下袭终之。而后二章至圣至诚。亦就此章而言其极致。其条理脉络。灿然可观也如此。尽乎其为圣人之言也。
中庸第三十一章
御制条问曰。中正与仁义对说。则中是大中之礼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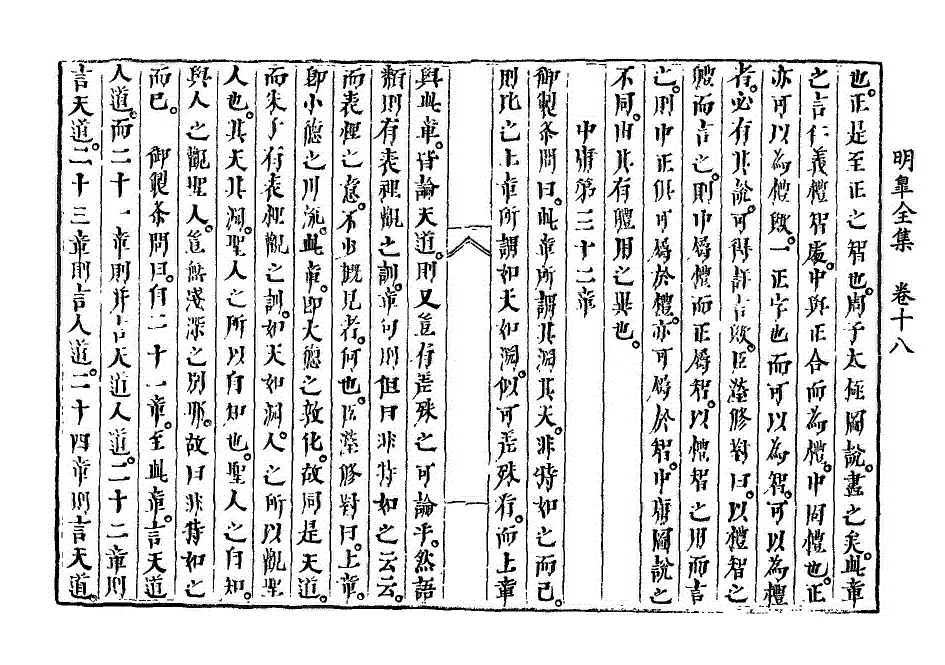 也。正是至正之智也。周子太极图说。尽之矣。此章之言仁义礼智处。中与正合而为礼。中固礼也。正亦可以为礼欤。一正字也而可以为智。可以为礼者。必有其说。可得详言欤。臣滢修对曰。以礼智之体而言之。则中属礼而正属智。以礼智之用而言之。则中正俱可属于礼。亦可属于智。中庸图说之不同。由其有体用之异也。
也。正是至正之智也。周子太极图说。尽之矣。此章之言仁义礼智处。中与正合而为礼。中固礼也。正亦可以为礼欤。一正字也而可以为智。可以为礼者。必有其说。可得详言欤。臣滢修对曰。以礼智之体而言之。则中属礼而正属智。以礼智之用而言之。则中正俱可属于礼。亦可属于智。中庸图说之不同。由其有体用之异也。中庸第三十二章
御制条问曰。此章所谓其渊其天。非特如之而已。则比之上章所谓如天如渊。似可差殊看。而上章与此章。皆论天道。则又岂有差殊之可论乎。然语类则有表里观之训。章句则但曰非特如之云云。而表里之意。不少概见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上章。即小德之川流。此章。即大德之敦化。故同是天道。而朱子有表里观之训。如天如渊。人之所以观圣人也。其天其渊。圣人之所以自知也。圣人之自知。与人之观圣人。岂无浅深之别耶。故曰非特如之而已。 御制条问曰。自二十一章。至此章。言天道人道。而二十一章则并言天道人道。二十二章则言天道。二十三章则言人道。二十四章则言天道。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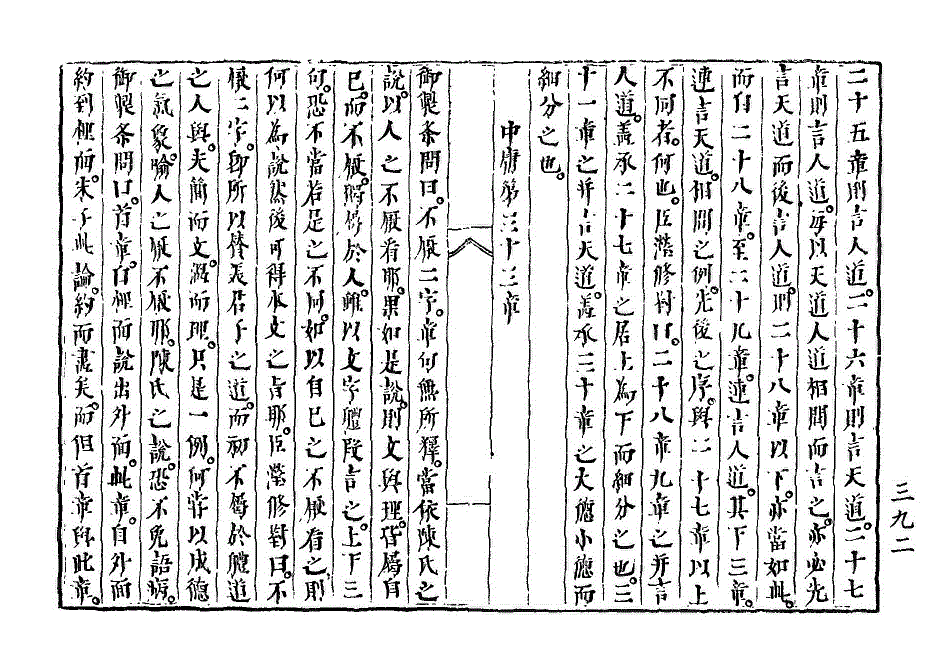 二十五章则言人道。二十六章则言天道。二十七章则言人道。每以天道人道相间而言之。亦必先言天道而后言人道。则二十八章以下。亦当如此。而自二十八章。至二十九章。连言人道。其下三章。连言天道。相间之例。先后之序。与二十七章以上不同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二十八章九章之并言人道。盖承二十七章之居上为下而细分之也。三十一章之并言天道。盖承三十章之大德小德而细分之也。
二十五章则言人道。二十六章则言天道。二十七章则言人道。每以天道人道相间而言之。亦必先言天道而后言人道。则二十八章以下。亦当如此。而自二十八章。至二十九章。连言人道。其下三章。连言天道。相间之例。先后之序。与二十七章以上不同者。何也。臣滢修对曰。二十八章九章之并言人道。盖承二十七章之居上为下而细分之也。三十一章之并言天道。盖承三十章之大德小德而细分之也。中庸第三十三章
御制条问曰。不厌二字。章句无所释。当依陈氏之说。以人之不厌看耶。果如是说。则文与理。皆属自己。而不厌。独属于人。虽以文字体段言之。上下三句。恐不当若是之不同。如以自己之不厌看之则何以为说然后可得本文之旨耶。臣滢修对曰。不厌二字。即所以赞美君子之道。而初不属于体道之人与。夫简而文。温而理。只是一例。何尝以成德之气象。喻人之厌不厌耶。陈氏之说。恐不免语病。御制条问曰。首章。自里而说出外面。此章。自外面约到里面。朱子此论。约而尽矣。而但首章与此章。
明皋全集卷之十八 第 393H 页
 各自有表里。恐不可谓首章为里。此章为表。亦不可谓此章为里。首章为表。则朱子之必以此章与首章谓相表里者。何也。臣滢修对曰。首章则自一理而散为万事。故由内而外不得不推将去。此章则自万事而末复合为一理。故由外而内不得不引向来。然由内及外。由外及内。其各自有表里则一也。何尝以两章。偏属之一边耶。 御制条问曰。首章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即无极而太极也。此章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即太极本无极也。胡氏此言。诚极允当。苟于此见得透彻。说得分晓。则三十三章之微辞奥旨。庶可以随处贯通。幸慎思而明卞之。臣滢修对曰。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者。顺推之说。而万物生出之序也。太极本无极者。逆推之说。而万物原本之论也。此篇首章。则自天命之性。以至于位天育物之极功。岂非所谓顺推之说乎。此章则自入德之方。以及乎无声无臭之微妙。岂非逆推之说乎。虽然。此特言其立言之次第耳。究其实则无极而太极云者。即所谓太极本无极也。亦岂有二理哉。
各自有表里。恐不可谓首章为里。此章为表。亦不可谓此章为里。首章为表。则朱子之必以此章与首章谓相表里者。何也。臣滢修对曰。首章则自一理而散为万事。故由内而外不得不推将去。此章则自万事而末复合为一理。故由外而内不得不引向来。然由内及外。由外及内。其各自有表里则一也。何尝以两章。偏属之一边耶。 御制条问曰。首章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即无极而太极也。此章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即太极本无极也。胡氏此言。诚极允当。苟于此见得透彻。说得分晓。则三十三章之微辞奥旨。庶可以随处贯通。幸慎思而明卞之。臣滢修对曰。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者。顺推之说。而万物生出之序也。太极本无极者。逆推之说。而万物原本之论也。此篇首章。则自天命之性。以至于位天育物之极功。岂非所谓顺推之说乎。此章则自入德之方。以及乎无声无臭之微妙。岂非逆推之说乎。虽然。此特言其立言之次第耳。究其实则无极而太极云者。即所谓太极本无极也。亦岂有二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