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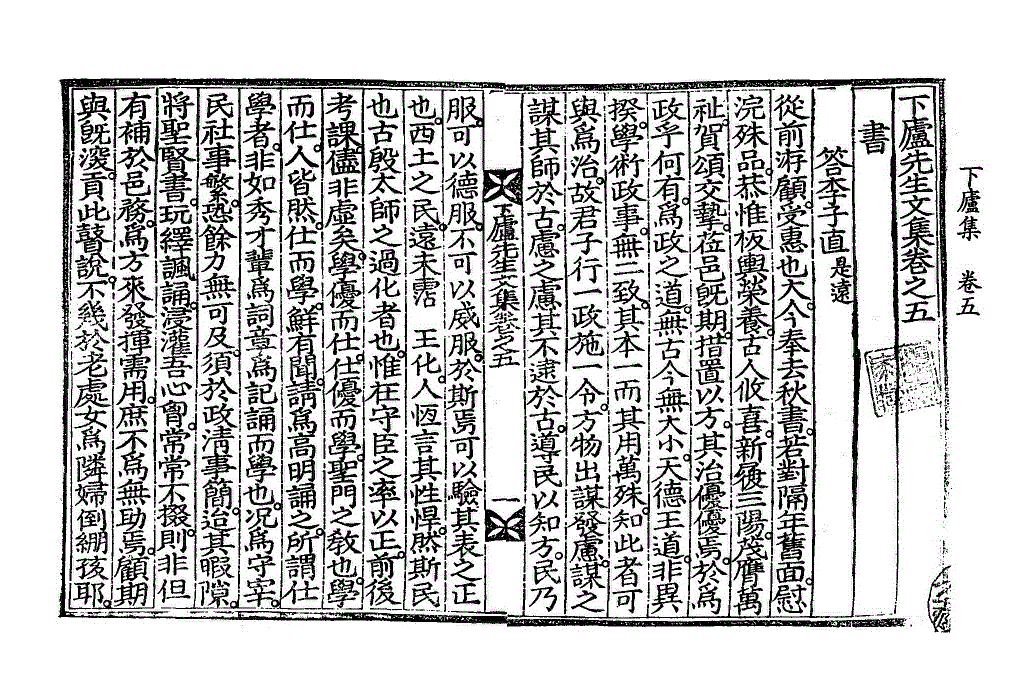 答李子直(是远)
答李子直(是远)从前荐顾。受惠也大。今奉去秋书。若对隔年旧面。慰浣殊品。恭惟板舆荣养。古人攸喜。新履三阳。茂膺万祉。贺颂交挚。莅邑既期。措置以方。其治优优焉。于为政乎何有。为政之道。无古今无大小。天德王道。非异揆。学术政事。无二致。其本一而其用万殊。知此者可与为治。故君子行一政施一令。方物出谋发虑。谋之谋其师于古。虑之虑其不逮于古。导民以知方。民乃服。可以德服。不可以威服。于斯焉可以验其表之正也。西土之民。远未沾 王化。人恒言其性悍。然斯民也古殷太师之过化者也。惟在守臣之率以正。前后考课。尽非虚矣。学优而仕。仕优而学。圣门之教也。学而仕。人皆然。仕而学。鲜有闻。请为高明诵之。所谓仕学者。非如秀才辈为词章为记诵而学也。况为守宰。民社事繁。恐馀力无可及。须于政清事简。迨其暇隙。将圣贤书。玩绎讽诵。浸灌吾心胸。常常不掇。则非但有补于邑务。为方来发挥需用。庶不为无助焉。顾期与既深。贡此瞽说。不几于老处女为邻妇倒绷孩耶。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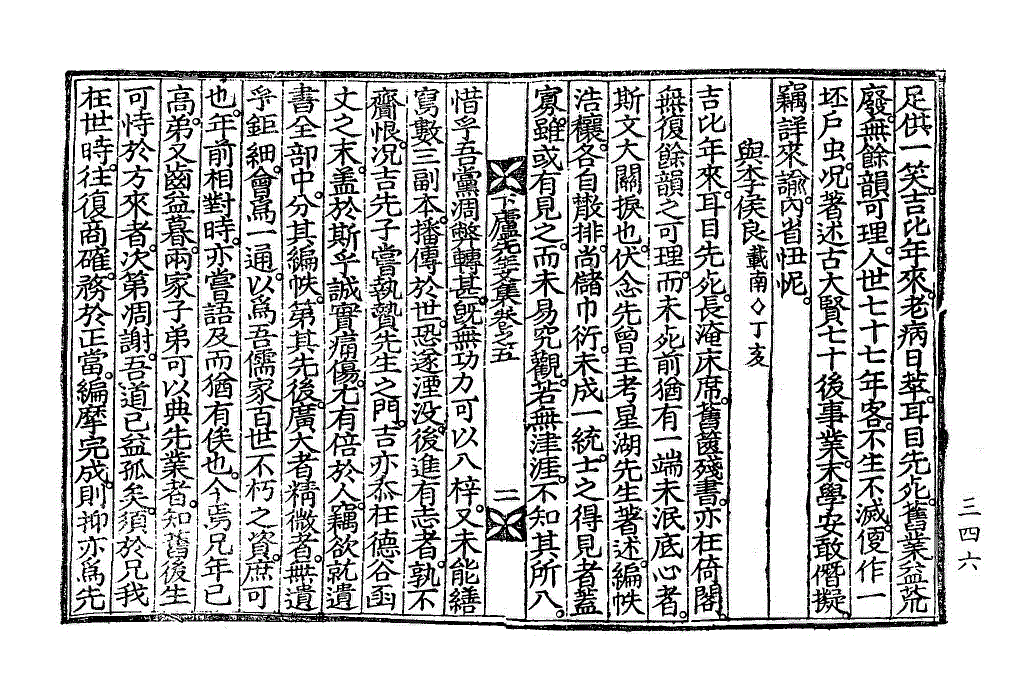 足供一笑。吉比年来。老病日萃。耳目先死。旧业益荒废。无馀韵可理。人世七十七年客。不生不灭。便作一坯户虫。况著述古大贤七十后事业。末学安敢僭拟。窃详来谕。内省忸怩。
足供一笑。吉比年来。老病日萃。耳目先死。旧业益荒废。无馀韵可理。人世七十七年客。不生不灭。便作一坯户虫。况著述古大贤七十后事业。末学安敢僭拟。窃详来谕。内省忸怩。与李侯良(载南○丁亥)
吉比年来。耳目先死。长淹床席。旧箧残书。亦在倚阁。无复馀韵之可理。而未死前犹有一端未泯底心者。斯文大关捩也。伏念先曾王考星湖先生著述。编帙浩穰。各自散排。尚储巾衍。未成一统。士之得见者盖寡。虽或有见之。而未易究观。若无津涯。不知其所入。惜乎吾党凋弊转甚。既无功力可以入梓。又未能缮写数三副本。播传于世。恐遂湮没。后进有志者。孰不赍恨。况吉先子尝执贽先生之门。吉亦忝在德谷函丈之末。盖于斯乎诚实痛伤。尤有倍于人。窃欲就遗书全部中。分其编帙。第其先后。广大者精微者。无遗乎钜细。会为一通。以为吾儒家百世不朽之资。庶可也。年前相对时。亦尝语及而犹有俟也。今焉兄年已高。弟又齿益暮。两家子弟可以典先业者。知旧后生可恃于方来者。次第凋谢。吾道已益孤矣。须于兄我在世时。往复商确。务于正当。编摩完成。则抑亦为先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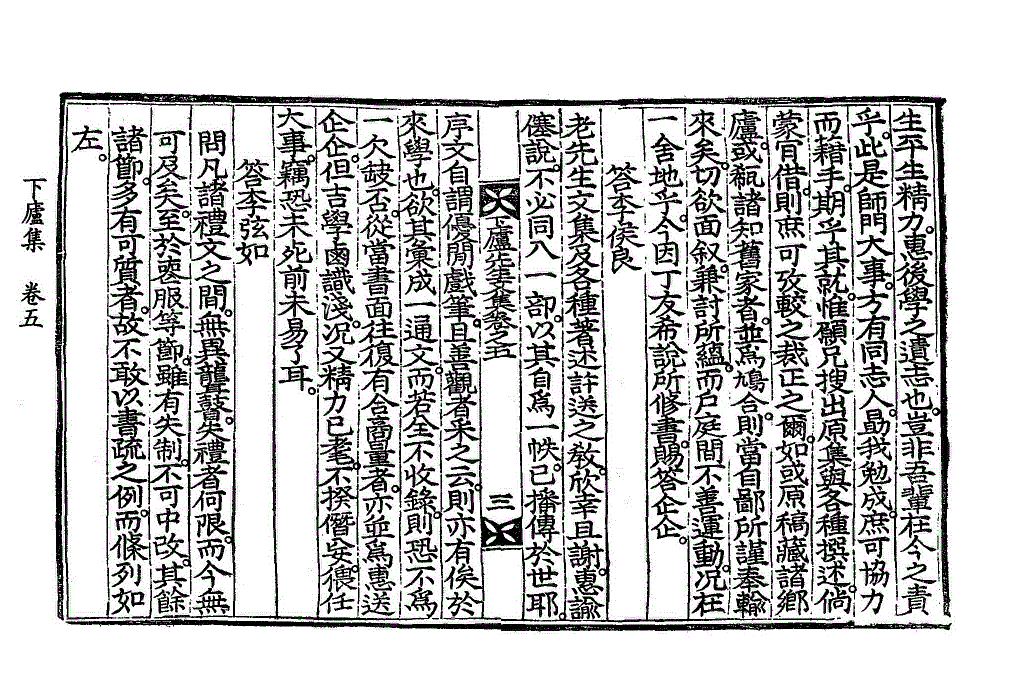 生平生精力。惠后学之遗志也。岂非吾辈在今之责乎。此是师门大事。方有同志人。勖我勉成。庶可协力而藉手。期乎其就。惟愿兄搜出原集与各种撰述。倘蒙肯借。则庶可考较之裁正之尔。如或原稿藏诸乡庐。或瓻诸知旧家者。并为鸠合。则当自鄙所谨奉输来矣。切欲面叙。兼讨所蕴。而户庭间不善运动。况在一舍地乎。今因丁友希说所修书。赐答企企。
生平生精力。惠后学之遗志也。岂非吾辈在今之责乎。此是师门大事。方有同志人。勖我勉成。庶可协力而藉手。期乎其就。惟愿兄搜出原集与各种撰述。倘蒙肯借。则庶可考较之裁正之尔。如或原稿藏诸乡庐。或瓻诸知旧家者。并为鸠合。则当自鄙所谨奉输来矣。切欲面叙。兼讨所蕴。而户庭间不善运动。况在一舍地乎。今因丁友希说所修书。赐答企企。答李侯良
老先生文集及各种著述许送之教。欣幸且谢。惠谕僿说。不必同入一部。以其自为一帙。已播传于世耶。序文自谓优閒戏笔。且善观者采之云。则亦有俟于来学也。欲其汇成一通文。而若全不收录。则恐不为一欠缺否。从当书面往复有合商量者。亦并为惠送企企。但吉学卤识浅。况又精力已耄。不揆僭妄。猥任大事。窃恐未死前未易了耳。
答李弦如
问凡诸礼文之间。无异聋瞽。失礼者何限。而今无可及矣。至于丧服等节。虽有失制。不可中改。其馀诸节。多有可质者。故不敢以书疏之例。而条列如左。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7L 页
 入棺时有大段错误事。想已闻知矣。每一念未安。事当改以他棺材。而议论不一。且事关重大。未知何以则可。
入棺时有大段错误事。想已闻知矣。每一念未安。事当改以他棺材。而议论不一。且事关重大。未知何以则可。拜宾受吊。乃主人之事。非众主人之事。则至于罪人出系之人。又有间于众主人之拜。家侄病未受吊。因废拜宾之礼。则亦非待宾之道。于此于彼。俱非稳当。所失轻重何如。
朝祖大礼也。宗家异室而稍远。则虽以魂帛铭旌。代行奉柩之仪。节次自多难便。姑从时俗欲停止。能无大害于礼否。
晨昏哭朝夕奠。自是两件事。而奠有有拜之文。晨昏无有拜之文。此乃沙溪备要中所见也。晨昏乃旧日定省之礼。则似有拜。而无拜何也。卒哭后无奠。则至于朝夕哭无拜可乎。
题主奠。古无其礼。今俗皆行之。虞祭则不出于葬日之内。又有日中之礼。若路远则于所馆行之。以其急于安神之意也。以臆见料之。题主奠既非古礼。虞祭为急。则当于题主后仍虞祭。似或近之。而既有返而虞之文。不可以意起欤。
埋魂帛。星湖有埋于墓庭之论。罪人家亦曾然矣。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8H 页
 礼言虞而后埋者。以其虞之前。未知神依于木主。故返哭时神主与魂帛。一例奉还。而虞后当埋何所耶。
礼言虞而后埋者。以其虞之前。未知神依于木主。故返哭时神主与魂帛。一例奉还。而虞后当埋何所耶。祔祭使宗子纸榜行祀。有寒冈,星湖之说。欲从此行之。而卒哭后有故未即行。当待小祥大祥。亦无害于礼否。
出系人于本生亲之丧。有谢答之书。当称之云何。孤哀之称似不可。只以罪人称之否。
俯询礼条。窃仰尊哀爱礼之意。然借睹于瞽。借听于聋。果能得其真的见闻乎。猥承辱问。愧悚交至。首一节。前因从氏有所云云。想已奉闻。此是猝当急遽之中。偶失先后之次。而事不至于大悖。则其于慎重之义。何敢猝然变改耶。受吊拜宾。檀弓曰大夫之庶子不受吊。贾疏曰适子受吊拜宾。或有故则庶子不敢受吊。士之庶子。得受吊也。星湖亦云子侄受吊。宜在后列。同时拜。亦恐无嫌。今尊哀家。当用士丧之礼。况是宗孙病未主事。则葬祭诸节。莫非尊哀之所摄行。其与子侄之后列。尤有别焉。拜宾以谢之礼。恐不可废也。朝祖之礼。殷朝而殡。周朝而遂葬。盖象平时出必告之义也。故记曰顺死者之孝心也。尝闻近世丧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8L 页
 不同宫则皆阙而不行。遂为谬例。恐是委巷之礼也。如非大妨事势。遵古行之。似为得宜。朝夕哭拜之说。朱子曰想只是父母生时。子弟欲拜。亦须待父母起而衣服。然则晨而入哭。因捲灵寝。即生时起而衣服之顷也。于斯焉恐不可无拜。至于夕哭。展寝拜退。亦象其事生之事也。虞后亦推例行之。虽至练后止哭。晨昏展拜。似不可阙也。题主奠。始于五礼仪。而其源则家礼炷香斟酒之仪也。后世之别设过丰。大失礼意。然而神主既成。且有告辞。则斟酒之仪。似未违礼。虞祭所以迎精而返。祭于殡宫以安之者也。古者日中而虞。故檀弓曰葬日而虞。不忍一日离也。既非途远日晚。径宿山下。则何可不遵古今之经礼耶。至于埋魂帛。杂记云重既虞而埋之。郑注云就所倚处埋之。今之魂帛。即古重之遗制也。所倚处。即开元礼所谓庙之北阶也。然今之庙制不备。则埋于墓庭。亦就其所倚之意也。祔祭之礼。礼云殷人练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程张诸贤。皆言三年而祔。至于朱子。断以从周之礼。则宜所遵用。而或有事故。蹉过时月。至练至三年。亦不为无据矣。出后人丧中书疏。古无考證。而星湖云罪人之称不可。当称期服丧人。又云称出后
不同宫则皆阙而不行。遂为谬例。恐是委巷之礼也。如非大妨事势。遵古行之。似为得宜。朝夕哭拜之说。朱子曰想只是父母生时。子弟欲拜。亦须待父母起而衣服。然则晨而入哭。因捲灵寝。即生时起而衣服之顷也。于斯焉恐不可无拜。至于夕哭。展寝拜退。亦象其事生之事也。虞后亦推例行之。虽至练后止哭。晨昏展拜。似不可阙也。题主奠。始于五礼仪。而其源则家礼炷香斟酒之仪也。后世之别设过丰。大失礼意。然而神主既成。且有告辞。则斟酒之仪。似未违礼。虞祭所以迎精而返。祭于殡宫以安之者也。古者日中而虞。故檀弓曰葬日而虞。不忍一日离也。既非途远日晚。径宿山下。则何可不遵古今之经礼耶。至于埋魂帛。杂记云重既虞而埋之。郑注云就所倚处埋之。今之魂帛。即古重之遗制也。所倚处。即开元礼所谓庙之北阶也。然今之庙制不备。则埋于墓庭。亦就其所倚之意也。祔祭之礼。礼云殷人练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程张诸贤。皆言三年而祔。至于朱子。断以从周之礼。则宜所遵用。而或有事故。蹉过时月。至练至三年。亦不为无据矣。出后人丧中书疏。古无考證。而星湖云罪人之称不可。当称期服丧人。又云称出后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9H 页
 丧人。犹为近之。二说庶为合宜耳。妄陈数条。未免臆说。幸须博访知礼之家。务归至当。折衷而行之。区区之望也。
丧人。犹为近之。二说庶为合宜耳。妄陈数条。未免臆说。幸须博访知礼之家。务归至当。折衷而行之。区区之望也。答李弦如(己酉)
来谕曰善始哀成服于今月十六日。越三日十九日。即其亡室小期也。葬前废祭。既有朱子之说。故祥祭不得设行于当日。后丧成服前。前丧朝夕奠上食当废。亦有沙溪之说。故成服后朝夕上食奠以素馔矣。祥祭不设则灵筵不可撤。灵筵不撤则当有朝夕上食。此不过参以情理而言耳。事系变礼。礼无可据。望须广考礼书。以破此惑如何。且仪礼则朝夕奠朝夕哭。自是两事。而善始家合设一时。谓以家礼。未知于礼有据否。示之。
考朱子说。葬前废祭有数条。答胡伯量书云荐新告朔。吉匈相袭。似不可行。未葬可废。窦文卿问未葬时遇先忌。当废祭否。朱子答。忌者丧之馀。祭似无嫌云云。以此推之。用吉之祭可废。而丧馀之祭。尚不为嫌。况此祥期。乃是丧礼之祭。难以一例废之也。抑又有可證者。权上舍某父在母丧中。遭本生祖母丧。母丧祥期在祖母丧未葬时。问诸星湖先生。答曰佥哀除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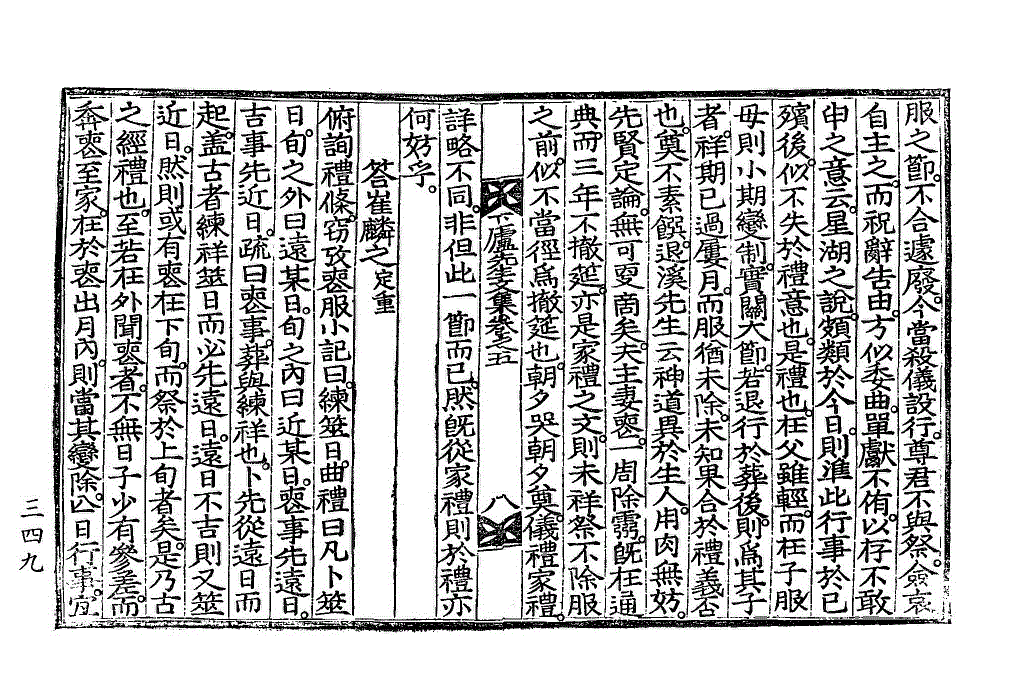 服之节。不合遽废。今当杀仪设行。尊君不与祭。佥哀自主之。而祝辞告由。方似委曲。单献不侑。以存不敢申之意云。星湖之说。颇类于今日。则准此行事于已殡后。似不失于礼意也。是礼也。在父虽轻。而在子服母则小期变制。实关大节。若退行于葬后。则为其子者。祥期已过屡月。而服犹未除。未知果合于礼义否也。奠不素馔。退溪先生云神道异于生人。用肉无妨。先贤定论。无可更商矣。夫主妻丧。一周除灵。既在通典。而三年不撤筵。亦是家礼之文。则未祥祭不除服之前。似不当径为撤筵也。朝夕哭朝夕奠。仪礼家礼。详略不同。非但此一节而已。然既从家礼则于礼亦何妨乎。
服之节。不合遽废。今当杀仪设行。尊君不与祭。佥哀自主之。而祝辞告由。方似委曲。单献不侑。以存不敢申之意云。星湖之说。颇类于今日。则准此行事于已殡后。似不失于礼意也。是礼也。在父虽轻。而在子服母则小期变制。实关大节。若退行于葬后。则为其子者。祥期已过屡月。而服犹未除。未知果合于礼义否也。奠不素馔。退溪先生云神道异于生人。用肉无妨。先贤定论。无可更商矣。夫主妻丧。一周除灵。既在通典。而三年不撤筵。亦是家礼之文。则未祥祭不除服之前。似不当径为撤筵也。朝夕哭朝夕奠。仪礼家礼。详略不同。非但此一节而已。然既从家礼则于礼亦何妨乎。答崔麟之(定重)
俯询礼条。窃考丧服小记曰。练筮日。曲礼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疏曰丧事。葬与练祥也。卜先从远日而起。盖古者练祥筮日而必先远日。远日不吉则又筮近日。然则或有丧在下旬。而祭于上旬者矣。是乃古之经礼也。至若在外闻丧者。不无日子少有参差。而奔丧至家。在于丧出月内。则当其变除。亡日行事。宜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0H 页
 以筮日为例也。星湖先生曰若闻讣见柩。不离月中。则只练祥于忌日。而除服于见柩日。礼以见柩当亡日故也。(星湖说止此)此论煞十分明白。窃恐无可改评矣。顾此謏闻寡见。固不足以博考详證。而不耻之问。不敢虚也。玆乃奉复。幸须广询于知礼家。折衷而行之。
以筮日为例也。星湖先生曰若闻讣见柩。不离月中。则只练祥于忌日。而除服于见柩日。礼以见柩当亡日故也。(星湖说止此)此论煞十分明白。窃恐无可改评矣。顾此謏闻寡见。固不足以博考详證。而不耻之问。不敢虚也。玆乃奉复。幸须广询于知礼家。折衷而行之。答崔麟之
俯询礼节。覼缕盈幅。敬玩再三。窃观读礼之功。弥深弥笃。为之钦诵殊品。谨按礼有税服之文。疏曰亲死道路既远。方始闻则税之。税之谓追服也。朱子所以有后满后除之论也。至若答曾无疑书。盖成服太晚者。与闻丧在后时。其例不同。来谕所云闻丧而成服者。以闻丧日象其始丧。奔丧而成服者。以奔丧日象其始丧者。诚然诚然。恐不可谓太晚之失也。礼奔丧者三日成服。疏曰谓来奔丧日后三日。通奔日则为四日。于此日成服。故家礼以至家后四日成服。以此推之则以见柩日准亡日。其义较然尔。来谕练有除服之义。礼疏亦有云云。然而星湖尝论之曰或疑主人不练服。而犹举期祭。则练为虚名。此盖以常道言也。期而当练。以名其祭。或因事变而当练不练。不之计也。纵曰主丧者不练其服。岂非当练之期乎。此说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0L 页
 煞明白矣。礼曰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死者之事。自始死数至三日而殡。生者之事。自死之明日成绖。亦数至三日而成服。三年而丧毕。即死与之事。三年而缞服除者。即生与之事。虽使适子不在。三日而不敢不殡。三月而不敢不葬。三年而丧毕。何以异是。生与死与。固不可相搀也。星湖亦曰诸子先服者先除。虽适子后服后除。与诸子之闻讣后时者无别。服练于朝馈之时。至于除缞。则依既葬奔丧者先之墓之例。必于墓所哭而除之。不敢以子之服而再祭也。由是论之。金氏庶子不敢祭之说。非所可论。变除之日。告事于朝馈。恐似合宜。盖祭不为除丧设故也。禫有就吉之礼。然尚有哭泣之节。未至于纯吉也。朱子犹许居丧者墨缞将庙事。故今礼丧内行祖庙忌祀。况乎有事于父母。缞虽未除。独自阙然。不几于礼胜者乎。金氏说恐推不去也。至于追服未满者。虽既练而己独未练。则犹行朝夕哭。实合情礼。诚如来谕矣。丧服大功章注曰大功布者。其锻治(一作冶)之功粗沽之。张子所谓煅练大功之布者。盖本于此。而图式仪节亦皆由是也。然礼曰父母之丧。十三月而练冠。又曰练。练衣黄里縓缘。疏曰小祥而著练冠练中衣。故曰练也。正服
煞明白矣。礼曰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死者之事。自始死数至三日而殡。生者之事。自死之明日成绖。亦数至三日而成服。三年而丧毕。即死与之事。三年而缞服除者。即生与之事。虽使适子不在。三日而不敢不殡。三月而不敢不葬。三年而丧毕。何以异是。生与死与。固不可相搀也。星湖亦曰诸子先服者先除。虽适子后服后除。与诸子之闻讣后时者无别。服练于朝馈之时。至于除缞。则依既葬奔丧者先之墓之例。必于墓所哭而除之。不敢以子之服而再祭也。由是论之。金氏庶子不敢祭之说。非所可论。变除之日。告事于朝馈。恐似合宜。盖祭不为除丧设故也。禫有就吉之礼。然尚有哭泣之节。未至于纯吉也。朱子犹许居丧者墨缞将庙事。故今礼丧内行祖庙忌祀。况乎有事于父母。缞虽未除。独自阙然。不几于礼胜者乎。金氏说恐推不去也。至于追服未满者。虽既练而己独未练。则犹行朝夕哭。实合情礼。诚如来谕矣。丧服大功章注曰大功布者。其锻治(一作冶)之功粗沽之。张子所谓煅练大功之布者。盖本于此。而图式仪节亦皆由是也。然礼曰父母之丧。十三月而练冠。又曰练。练衣黄里縓缘。疏曰小祥而著练冠练中衣。故曰练也。正服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1H 页
 不可变。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盖记礼者。详言练冠练中衣。而独不及于缞。则缞之不练可知也。退溪所云非谓并练缞者是已。吉年前遭艰时。至练而缞服破坏已甚。未免别制。而依正服不变之礼。不之练也。至于妇服则用家礼文不为别制。去负版辟领衰。截长裙而已。盖先兄之酌定者也。家礼练服为冠之服字。星湖以为或衍或布字之误。来谕得之矣。绖带熟麻。古无其礼。东俗未知出于何时。而始见于备要。虽云代葛而服于练时。已失卒哭受葛之义。仪节言练而服葛。而寒冈谓之盖晚矣。家礼不言改麻绖。则以麻终三年也。卒哭既未受葛。则恐不若遵用家礼之为有据也。斩衰虞后变麻服布。其说甚长。请略言之。丧服传曰绞带者。绳带也。冠绳缨条属。疏曰绖带至虞后变麻服葛。绞带虞后虽不言变。按公士众臣为君服布带。又齐衰以下亦布带。则绞带虞后变麻服布则于义可也。勉斋图式亦以是而谓之变麻服布。七升布为之。窃尝致疑。谛观传文。则绳带与绳缨并称。而斩衰练冠。犹用绳缨。而非布武。则奚独于绳带。以齐衰布带之故。变绳服布乎。又考丧服齐衰章曰。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注云公卿大
不可变。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盖记礼者。详言练冠练中衣。而独不及于缞。则缞之不练可知也。退溪所云非谓并练缞者是已。吉年前遭艰时。至练而缞服破坏已甚。未免别制。而依正服不变之礼。不之练也。至于妇服则用家礼文不为别制。去负版辟领衰。截长裙而已。盖先兄之酌定者也。家礼练服为冠之服字。星湖以为或衍或布字之误。来谕得之矣。绖带熟麻。古无其礼。东俗未知出于何时。而始见于备要。虽云代葛而服于练时。已失卒哭受葛之义。仪节言练而服葛。而寒冈谓之盖晚矣。家礼不言改麻绖。则以麻终三年也。卒哭既未受葛。则恐不若遵用家礼之为有据也。斩衰虞后变麻服布。其说甚长。请略言之。丧服传曰绞带者。绳带也。冠绳缨条属。疏曰绖带至虞后变麻服葛。绞带虞后虽不言变。按公士众臣为君服布带。又齐衰以下亦布带。则绞带虞后变麻服布则于义可也。勉斋图式亦以是而谓之变麻服布。七升布为之。窃尝致疑。谛观传文。则绳带与绳缨并称。而斩衰练冠。犹用绳缨。而非布武。则奚独于绳带。以齐衰布带之故。变绳服布乎。又考丧服齐衰章曰。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注云公卿大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1L 页
 夫。厌于天子诸侯。故降其众臣而布带绳屦。贵臣得伸。不夺其正。盖公士大夫之众臣则厌降而布带。其贵臣犹为不降于正服。况乎为父之斩衰。而其可比拟于众臣之厌降耶。经中既无变绞之文。而贾氏援引为證。既失其类矣。夫为父斩为母齐。括免缨带。一麻一布。已有定制。不可相混者。而疏说所谓于义可也一句。既非定论。而特以志其疑也。至若图式杨信斋亦谓草具甫就。未及證正而殁者。殆此之类欤。盖服之当变者。如缞绖等是也。经文既详说复言。而何尝一言及于变绞带耶。备要小祥条。备录疏说。殆若定礼。世或有从之者。窃尝求其说而未得也。星湖曰既无事于卒哭。乃欲变布于练。用意尤涉斑驳。不可从。可谓折衷之论也。今俗丧中方笠直领等。即出入时服。而古墨衰之义也。好礼之家。虽斩衰既虞。则绞带不敢加于墨衰。故别制布带。与变麻服布者。亦异矣。未知尊哀意下如何。
夫。厌于天子诸侯。故降其众臣而布带绳屦。贵臣得伸。不夺其正。盖公士大夫之众臣则厌降而布带。其贵臣犹为不降于正服。况乎为父之斩衰。而其可比拟于众臣之厌降耶。经中既无变绞之文。而贾氏援引为證。既失其类矣。夫为父斩为母齐。括免缨带。一麻一布。已有定制。不可相混者。而疏说所谓于义可也一句。既非定论。而特以志其疑也。至若图式杨信斋亦谓草具甫就。未及證正而殁者。殆此之类欤。盖服之当变者。如缞绖等是也。经文既详说复言。而何尝一言及于变绞带耶。备要小祥条。备录疏说。殆若定礼。世或有从之者。窃尝求其说而未得也。星湖曰既无事于卒哭。乃欲变布于练。用意尤涉斑驳。不可从。可谓折衷之论也。今俗丧中方笠直领等。即出入时服。而古墨衰之义也。好礼之家。虽斩衰既虞。则绞带不敢加于墨衰。故别制布带。与变麻服布者。亦异矣。未知尊哀意下如何。答崔麟之
问今日即先兄忌日。而先兄之聘君。月前丧逝。在未葬中。丘嫂之配设受享。于人情神理。俱为未安。故初意则欲为单设所祭主而已矣。更思之则忌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2H 页
 日丧馀。自异于时享吉事。从夫配食。不悖于义理。故果以并设行之。未知如何。若遇时享吉祭则废之如何。而或有先辈之论此等事耶。人情之所不安处。亦神理之不安处。此必有义起底道理。不敢臆说。第此奉质。望赐回教。
日丧馀。自异于时享吉事。从夫配食。不悖于义理。故果以并设行之。未知如何。若遇时享吉祭则废之如何。而或有先辈之论此等事耶。人情之所不安处。亦神理之不安处。此必有义起底道理。不敢臆说。第此奉质。望赐回教。谨考旅轩答门人之问曰。祖父母初丧之日。设行父母忌祀。果为未安。不行何伤。若有他昆弟。略措素馔。行之别处。其或可乎。或问有子女先父母死。及父母丧未葬前。其忌祭墓祭。皆可废耶。愚伏曰未葬前废之无疑。窃为参考两先生之意。则忌是丧馀。且丧在异宫者。似当设行。至若时享墓祭。则似不可行。惟在意下酌宜处之耳。
答李伯游(滢夏○丙子)
问殇儿虽未成人。年既十四而夭。以情以礼。不可不立主。亦蒙教意。昨已造成。将于朔日奠。兼行题主。而陷中及粉面所题。不无疑错。既无冠名。又无字。则所题者儿名而已。遭戚时棺上铭旌。书以童蒙完山李某(儿名)之柩。今考礼说。童子之丧。题主皆以秀才云云。而无童蒙云云之称。乃知铭旌之书。殊失礼意。今此题主以秀才书之可乎。抑或棺上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2L 页
 所题与神主所题。有异同之嫌。依前以童蒙书之可乎。
所题与神主所题。有异同之嫌。依前以童蒙书之可乎。古礼未冠则不命字而只小字。宜以小字题其主。陷中书姓贯非古也。星湖先生曰中国姓谱。如李出陇西。柳出河东。更无如我东之多歧。则不必书。故礼中阙之。(星湖说止此)东人则虽知礼家。多书姓贯。至于妇人则必书以别之。已成例矣。书之亦何妨于礼。童子之丧。称公称讳。既有寒冈先生之定论。而其曰不敢的知云者。不以礼自处之谦辞也。后人之所不敢改评者矣。且星湖云礼言陷中不改。不改则易世而犹存。岂以今日之卑幼。不书讳字。称公称讳。亦何嫌焉。秀才之称。亦有自来矣。程子主式称号。谓处士秀才之类。故家礼题主条。以生时所称为号。盖秀才者。年少文艺之称也。今之既冠娶者无官则皆称学生。惟未冠者号以秀才。父虽主丧。生时称号。未必改也。卑幼题主则书名礼也。丘仪亦详之。后世阙其名者。未知何据也。铭旌题主。礼无异同。而古之人或有以地名堂号逸人野人等字。表诸铭旌及墓石者。其题主则似不然矣。今之改以秀才。恐非大违于礼也。幸须博访于当世知礼者。无或差失。区区之望也。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3H 页
 答李▣▣(游夏○甲申)
答李▣▣(游夏○甲申)问原州金侄济益。即侍生之表从子也。伯表叔无子。而季叔只有一子。取以为子。而季叔更不他养。以一子奉两家祀。此事世多有之。表从独身。幸有三子。长则自为大宗奉祀孙。次则还归本家为本家奉祀孙。近来表从内外俱殁。其长子亦早世。季表叔母与次侄济益。相依为命。今当季表叔母之丧。丧既无主。服不过期。于情于礼。未知如何。乡中不无谤议。济益用是忧惧。才过襄礼。即走京师。将以仰质于门下。何如可以尽于情合于礼。而不得罪于乡党耶。伏望博考详教焉。
俯询出后孙服制加隆之礼。既无经礼可考。则后生末学。何敢冒犯汰哉之诮而轻为论定耶。闻京乡士友家。或服三年或服期云。则未知其有何所据经礼而然耶。既有可据则礼是一定之三尺。而不可参差。或期或三年之不同。抑何也。古之礼家。或如此或如彼。而各从其说耶。三年者。嫡孙承重服也。出后孙于何有承重之义。期年者。出后子之服。代其父者也。惟承重者代服。其义则非代父之服。而乃承祖之重也。既非嫡孙。且无重之可承。则其义何据。上自仪礼下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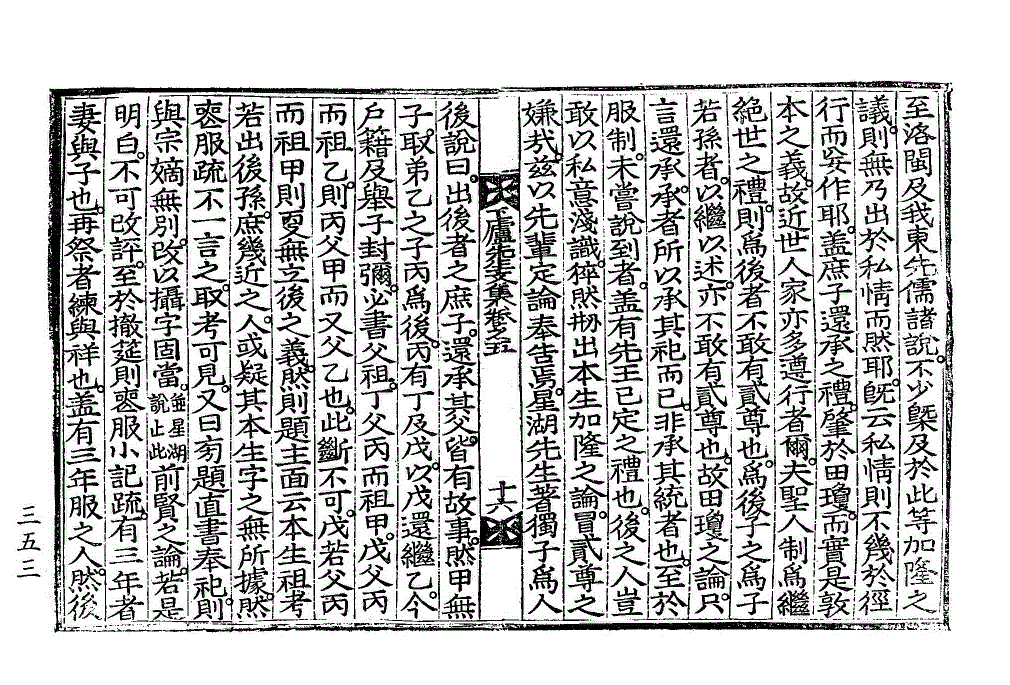 至洛闽及我东先儒诸说。不少槩及于此等加隆之议。则无乃出于私情而然耶。既云私情则不几于径行而妄作耶。盖庶子还承之礼。肇于田琼。而实是敦本之义。故近世人家亦多遵行者尔。夫圣人制为继绝世之礼。则为后者不敢有贰尊也。为后子之为子若孙者。以继以述。亦不敢有贰尊也。故田琼之论。只言还承。承者所以承其祀而已。非承其统者也。至于服制。未尝说到者。盖有先王已定之礼也。后之人岂敢以私意浅识。猝然刱出本生加隆之论。冒贰尊之嫌哉。玆以先辈定论奉告焉。星湖先生著独子为人后说曰。出后者之庶子。还承其父。皆有故事。然甲无子。取弟乙之子丙为后。丙有丁及戊。以戊还继乙。今户籍及举子封弥。必书父祖。丁父丙而祖甲。戊父丙而祖乙。则丙父甲而又父乙也。此断不可。戊若父丙而祖甲则更无立后之义。然则题主面云本生祖考若出后孙。庶几近之。人或疑其本生字之无所据。然丧服疏不一言之。取考可见。又曰旁题直书奉祀。则与宗嫡无别。改以摄字固当。(并星湖说止此)前贤之论。若是明白。不可改评。至于撤筵则丧服小记疏。有三年者妻与子也。再祭者练与祥也。盖有三年服之人。然后
至洛闽及我东先儒诸说。不少槩及于此等加隆之议。则无乃出于私情而然耶。既云私情则不几于径行而妄作耶。盖庶子还承之礼。肇于田琼。而实是敦本之义。故近世人家亦多遵行者尔。夫圣人制为继绝世之礼。则为后者不敢有贰尊也。为后子之为子若孙者。以继以述。亦不敢有贰尊也。故田琼之论。只言还承。承者所以承其祀而已。非承其统者也。至于服制。未尝说到者。盖有先王已定之礼也。后之人岂敢以私意浅识。猝然刱出本生加隆之论。冒贰尊之嫌哉。玆以先辈定论奉告焉。星湖先生著独子为人后说曰。出后者之庶子。还承其父。皆有故事。然甲无子。取弟乙之子丙为后。丙有丁及戊。以戊还继乙。今户籍及举子封弥。必书父祖。丁父丙而祖甲。戊父丙而祖乙。则丙父甲而又父乙也。此断不可。戊若父丙而祖甲则更无立后之义。然则题主面云本生祖考若出后孙。庶几近之。人或疑其本生字之无所据。然丧服疏不一言之。取考可见。又曰旁题直书奉祀。则与宗嫡无别。改以摄字固当。(并星湖说止此)前贤之论。若是明白。不可改评。至于撤筵则丧服小记疏。有三年者妻与子也。再祭者练与祥也。盖有三年服之人。然后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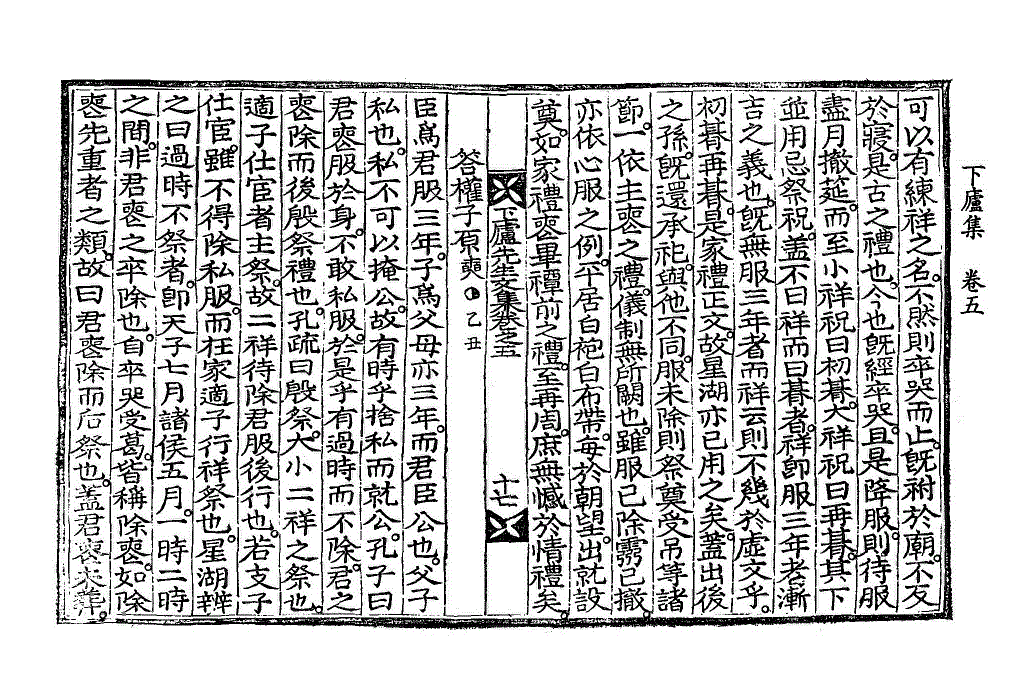 可以有练祥之名。不然则卒哭而止。既祔于庙。不反于寝。是古之礼也。今也既经卒哭。且是降服。则待服尽月撤筵。而至小祥祝曰初期。大祥祝曰再期。其下并用忌祭祝。盖不曰祥而曰期者。祥即服三年者渐吉之义也。既无服三年者而祥云则不几于虚文乎。初期再期。是家礼正文。故星湖亦已用之矣。盖出后之孙。既还承祀。与他不同。服未除则祭奠受吊等诸节。一依主丧之礼。仪制无所阙也。虽服已除灵已撤。亦依心服之例。平居白袍白布带。每于朝望。出就设奠。如家礼丧毕禫前之礼。至再周。庶无憾于情礼矣。
可以有练祥之名。不然则卒哭而止。既祔于庙。不反于寝。是古之礼也。今也既经卒哭。且是降服。则待服尽月撤筵。而至小祥祝曰初期。大祥祝曰再期。其下并用忌祭祝。盖不曰祥而曰期者。祥即服三年者渐吉之义也。既无服三年者而祥云则不几于虚文乎。初期再期。是家礼正文。故星湖亦已用之矣。盖出后之孙。既还承祀。与他不同。服未除则祭奠受吊等诸节。一依主丧之礼。仪制无所阙也。虽服已除灵已撤。亦依心服之例。平居白袍白布带。每于朝望。出就设奠。如家礼丧毕禫前之礼。至再周。庶无憾于情礼矣。答权子原(奭○乙丑)
臣为君服三年。子为父母亦三年。而君臣公也。父子私也。私不可以掩公。故有时乎舍私而就公。孔子曰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于是乎有过时而不除。君之丧除而后殷祭礼也。孔疏曰殷祭。大小二祥之祭也。适子仕宦者主祭。故二祥待除君服后行也。若支子仕宦。虽不得除私服。而在家适子行祥祭也。星湖辨之曰过时不祭者。即天子七月诸侯五月。一时二时之间。非君丧之卒除也。自卒哭受葛。皆称除丧。如除丧先重者之类。故曰君丧除而后祭也。盖君丧未葬。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4L 页
 则虽过时月。私丧不敢除。必待君丧卒哭之除。而始行私丧之二祥。此固大夫服君斩之礼也。或非大夫或大夫。而非适子。或后妃之丧。则皆不在此例也。周礼王后之丧。大夫士齐衰期。贾疏曰士之子贱无服。当从庶人礼。朱子君臣服议曰。参度人情。分别贵贱之等。以为隆杀之节者也。退溪曰 国之内丧与 国君丧亦有间。卒哭前时祭不可行。忌祭可行。星湖亦曰凡君夫人之丧未殡。准曾子问不得成礼之训。悉废大小祀典可也。殡后。忌日二祥之类。皆无可废之义。又曰二祥匈礼。不胙不旅。比特牲小牢已简。而不缛不侑酳不胙。据未殡而言。酒至三献。又未见其大妨。盖二祥丧祭也。忌亦丧之馀也。先贤皆据古礼而论之。故如是云尔。然礼之用。时为大。从周之义也。五礼仪 国恤卒哭后。大中小祀皆许行。来谕所云近世士大夫祥祭。皆退行卒哭后者。盖以此也。抑未知 国制只言 国家祀典欤。闾巷私祀。亦并在其中欤。窃闻 因山既定则许民窆葬。许葬则当许虞祔。虞祔亦丧祭也。祥亦似无异例。且易月公除。后晋虞潭祭庙。庙祭吉事。故庾蔚之讥之。若丧祭则似不然耳。第举国臣民。同在缟素之中。皆不敢除丧祥祭。
则虽过时月。私丧不敢除。必待君丧卒哭之除。而始行私丧之二祥。此固大夫服君斩之礼也。或非大夫或大夫。而非适子。或后妃之丧。则皆不在此例也。周礼王后之丧。大夫士齐衰期。贾疏曰士之子贱无服。当从庶人礼。朱子君臣服议曰。参度人情。分别贵贱之等。以为隆杀之节者也。退溪曰 国之内丧与 国君丧亦有间。卒哭前时祭不可行。忌祭可行。星湖亦曰凡君夫人之丧未殡。准曾子问不得成礼之训。悉废大小祀典可也。殡后。忌日二祥之类。皆无可废之义。又曰二祥匈礼。不胙不旅。比特牲小牢已简。而不缛不侑酳不胙。据未殡而言。酒至三献。又未见其大妨。盖二祥丧祭也。忌亦丧之馀也。先贤皆据古礼而论之。故如是云尔。然礼之用。时为大。从周之义也。五礼仪 国恤卒哭后。大中小祀皆许行。来谕所云近世士大夫祥祭。皆退行卒哭后者。盖以此也。抑未知 国制只言 国家祀典欤。闾巷私祀。亦并在其中欤。窃闻 因山既定则许民窆葬。许葬则当许虞祔。虞祔亦丧祭也。祥亦似无异例。且易月公除。后晋虞潭祭庙。庙祭吉事。故庾蔚之讥之。若丧祭则似不然耳。第举国臣民。同在缟素之中。皆不敢除丧祥祭。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5H 页
 而哀家若违众独行。则恐或致骇。幸须广询礼家。博访时议。参酌裁定。则朱子所云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者是也。未知哀意如何。尝闻甲辰 大丧时。徐花潭独言儒生只白衣冠三年。君丧岂可无服。遂齐衰三月。即仪礼经文也。然当时犹或议之。后贤亦莫之述焉。虽与此殊科。随时之义。亦不可不谛审也。惟哀谅之。
而哀家若违众独行。则恐或致骇。幸须广询礼家。博访时议。参酌裁定。则朱子所云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者是也。未知哀意如何。尝闻甲辰 大丧时。徐花潭独言儒生只白衣冠三年。君丧岂可无服。遂齐衰三月。即仪礼经文也。然当时犹或议之。后贤亦莫之述焉。虽与此殊科。随时之义。亦不可不谛审也。惟哀谅之。答李▣▣(明羲)
礼曰凡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朱子答陈安卿书曰。所问主祭事。据礼合以甲之长孙为之。若其不能则以目今尊长摄行可也。异时甲之长孙长成。却改正不妨。尊家今日之礼。与此数段。虽是异例。抑亦为傍准依据之地。亚府台监既主丧。则以其长者也亲者也。葬而题主。祭而祝辞。皆当主之。而但题主不曰奉祀。而曰摄祀。祝辞不曰孝子。而曰摄祀子。待三年丧毕则令从氏当长成。为之代摄。所以代摄者。以其宗子之介子。而摄祀于宗子故也。夫如是则庶几不悖于圣贤三尺之义乎否。
答李季受(益运)
问祢位既以摄祀子傍题。妣位合椟时。不可不依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5L 页
 此改题。而祖曾祖诸位。亦当此例耶。亡伯兄前以亡子某具讳题主而无傍题。今则诸议以为以显伯兄题主当然云。此果无害于礼意耶。若以显伯兄改题则傍题亦何以为之耶。亡伯兄有十三岁儿子。事当依例主祀。而渠亦是次子。则长侄立后前当。以摄祀傍题。未成人之以摄祀傍题。事甚如何。亦所不忍。议论多端。玆敢仰质。量教幸甚。且有亡长侄而初以亡孙某题主。姑未立后。立后前以亡侄改题。未知如何。
此改题。而祖曾祖诸位。亦当此例耶。亡伯兄前以亡子某具讳题主而无傍题。今则诸议以为以显伯兄题主当然云。此果无害于礼意耶。若以显伯兄改题则傍题亦何以为之耶。亡伯兄有十三岁儿子。事当依例主祀。而渠亦是次子。则长侄立后前当。以摄祀傍题。未成人之以摄祀傍题。事甚如何。亦所不忍。议论多端。玆敢仰质。量教幸甚。且有亡长侄而初以亡孙某题主。姑未立后。立后前以亡侄改题。未知如何。俯询礼条。礼之变节也。既无经传之可据。顾此謏闻寡识。固何敢率易證定。以犯汰哉之讥乎。窃观星湖先生答洪某书曰。先大夫主面傍题。既题以摄祀。则先夫人主面。不可因存亡室字。前贤既有定礼。则今于吉祭当依例改题。若祖曾祖诸位。一例改题。则似涉未安。退溪先生曰支子虽权宜杀礼而祭祢。亦未可及祖。盖宗法至重。祭犹不可及于祖。则改祭摄祀。亦未可轻易行之也。于显兄题主则以弟某傍注者。前人已有行者。然而是乃兄既无后而弟及之礼也。先伯氏台监既有次子。则虽未及长成。即宗子之介子。而他日摄祀者也。固不可用弟及之礼也。凡于祀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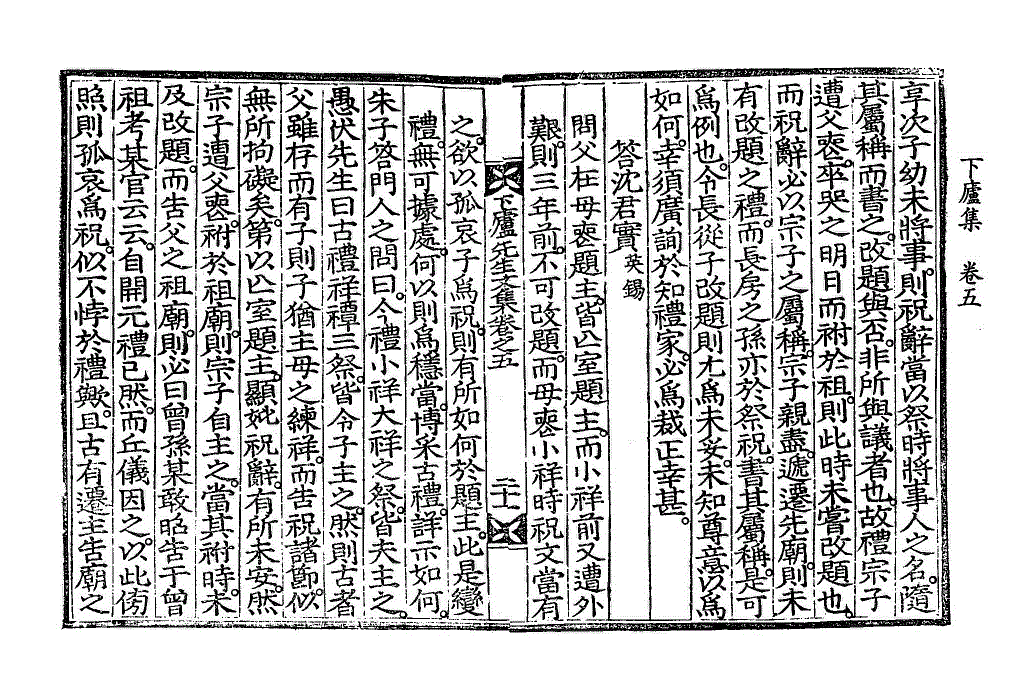 享次子幼未将事。则祝辞当以祭时将事人之名。随其属称而书之。改题与否。非所与议者也。故礼宗子遭父丧。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则此时未尝改题也。而祝辞必以宗子之属称。宗子亲尽。递迁先庙。则未有改题之礼。而长房之孙亦于祭祝。书其属称。是可为例也。令长从子改题则尤为未妥。未知尊意以为如何。幸须广询于知礼家。必为裁正幸甚。
享次子幼未将事。则祝辞当以祭时将事人之名。随其属称而书之。改题与否。非所与议者也。故礼宗子遭父丧。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则此时未尝改题也。而祝辞必以宗子之属称。宗子亲尽。递迁先庙。则未有改题之礼。而长房之孙亦于祭祝。书其属称。是可为例也。令长从子改题则尤为未妥。未知尊意以为如何。幸须广询于知礼家。必为裁正幸甚。答沈君实(英锡)
问父在母丧题主。皆亡室题主。而小祥前又遭外艰。则三年前。不可改题。而母丧小祥时祝文当有之。欲以孤哀子为祝。则有所如何于题主。此是变礼。无可据处。何以则为稳当。博采古礼。详示如何。
朱子答门人之问曰。今礼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愚伏先生曰古礼祥禫三祭。皆令子主之。然则古者父虽存而有子则子犹主母之练祥。而告祝诸节。似无所拘碍矣。第以亡室题主。显妣祝辞。有所未安。然宗子遭父丧。祔于祖庙。则宗子自主之。当其祔时。未及改题。而告父之祖庙。则必曰曾孙某敢昭告于曾祖考某官云云。自开元礼已然。而丘仪因之。以此傍照则孤哀为祝。似不悖于礼欤。且古有迁主告庙之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6L 页
 礼。(详见曾子问)故郑康成曰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庙。无主则以其币告之。若遭外艰时。即行告庙之礼。则练祥时诸节。尤无所碍耳。率易之对。未免汰哉。幸须博访知礼家。商处之。是企是企。
礼。(详见曾子问)故郑康成曰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庙。无主则以其币告之。若遭外艰时。即行告庙之礼。则练祥时诸节。尤无所碍耳。率易之对。未免汰哉。幸须博访知礼家。商处之。是企是企。答吴文初(瑸)
问父在母丧。十五月禫后。本生父母小祥后。皆心丧也。着缁笠带。而巾之有无黑白。未知何据欤。
今之布巾。即家礼之头𢄼。古免之遗。而所以敛发之具也。国俗惟丧则用之。故曰孝巾。或曰丧巾。既祥而白布笠。既禫而黪布笠。出后子既期而黪布笠。则服既除矣。似不可复用于渐吉之时矣。若家礼之黪布幞头。丘氏仪之布裹帽布用巾则当时平居之冠。而如东人之笠子故也。近世行礼之家。既祥而用笠则不复巾。故星湖先生曰某居忧时。入先庙则废头巾而用布网巾。然则虽丧笠之下。巾可以不用矣。今之人平居欲为从便。或有布制毛帽样。祥而用白。禫而用缁。以为常着掩髻之用。既非古制。又非冠非巾则有何礼之可据耶。
父在母丧及为本生父母心丧者。至二十五月而再期。则变制服未知何据耶。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7H 页
 父在为母及为本生父母心服终丧除服之节。古无其文。星湖先生曰父在为母除丧。则丘氏仪及 国制。祥祭白布笠白布衫带。至禫方缁其笠带。至再期则又不可无变动之节。用白布道袍白布带白布行縢。至二十七月而吉。心制则二十七月内哀未已也。(详载礼式)为本生亲者。既无练无禫。则初期而用父在为母之禫服。再期以后则同是心制。只依父在为母之变制则庶乎其可也。盖父在为母。古礼只云伸心丧。为本生父母。宋服制令始许伸心丧云。故后之言礼者。本生亲心丧。必傍照于父在为母之心丧。为之裁节之也。
父在为母及为本生父母心服终丧除服之节。古无其文。星湖先生曰父在为母除丧。则丘氏仪及 国制。祥祭白布笠白布衫带。至禫方缁其笠带。至再期则又不可无变动之节。用白布道袍白布带白布行縢。至二十七月而吉。心制则二十七月内哀未已也。(详载礼式)为本生亲者。既无练无禫。则初期而用父在为母之禫服。再期以后则同是心制。只依父在为母之变制则庶乎其可也。盖父在为母。古礼只云伸心丧。为本生父母。宋服制令始许伸心丧云。故后之言礼者。本生亲心丧。必傍照于父在为母之心丧。为之裁节之也。二十七月而禫。退溪先生曰纯吉未安。只依丘氏素服而祭。又曰不依大小祥陈服易服之节。未知禫服除在何节。吉服着在何日。愚伏曰礼曰禫而纤。盖吉祭之前。禫祭虽竟。尚纤冠素端黄裳。沙溪曰禫乃吉祭也。不可不服吉。又曰禫祭着纯吉之服。祭讫着微吉之服。而退溪所答。前后不同。未知何服为定云云。禫着吉服。禫后素服而尽其月后吉服云云。而皆从心服之制者。未知何据。而礼疑从厚而然欤。沙溪又曰粗黑笠。代古之纤冠。而虽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7L 页
 着素端白带则似过云云。
着素端白带则似过云云。禫服变制。前儒之论备矣。李子曰只依丘氏素服而祭云者。古礼既难尽复。则从先进之意也。又曰未知除服在何日云者。家礼既未详备。则及阙文之意也。寒冈先生曰禫服鄙生则仿家礼以黪色为笠子。带用白布。网巾用黪布。当时皆禀于李先生而为之。星湖先生曰此是退溪后来定论。世之言礼者。未及遍考。而乃以为前后所答不同。未知何服为定云者何也。沙溪禫着纯吉。祭讫微吉之说。推演杂记之疏。愚伏禫祭虽竟。纤冠黄裳之说。遵守间传之疏。窃考丧服图式则卒哭练祥禫。皆有受服变制之节。就其祥禫而言之。祥祭朝服缟冠。祥讫素缟麻衣。禫祭玄冠黄裳。禫讫朝服綅冠。古礼然也。及至后世。文质异宜。因时损益。固难以一从古制。故朱子家礼。于是乎因书仪而节取于仪礼。删其繁也。取其简也。受服变制之节。槩未之及焉。惟小祥云练服为冠。大祥云黪纱幞头黪布衫布裹带。禫只云如大祥之仪。盖取诸夫子宁俭之义也。至于我东。李子及寒冈星湖诸先生。遵述家礼。参以丘仪及 国制而行之。若其祥而白冠带。古之缟也。禫而缁冠带。古之纤也。祥而白则至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8H 页
 于禫而始变其缁。禫而缁则终其月而始就其吉。其间未尝有他变制之服。则从宜而不泥于古。从简而不至于野。后之言礼者。无可改评矣。沙溪所云禫祭服纯吉。终涉可疑。杂记郑注曰禫祭玄衣黄裳。黄裳者未大吉也。间传贾疏曰吉祭以后始从吉。若吉祭在禫月。犹未纯吉。然则禫之纯吉。于古无稽。故家礼禫章亦无吉服之文。则不为纯吉者明矣。沙溪备要禫祭条添入陈吉服三字。又于大祥条释之曰禫祭着吉服。今人丧礼。既未博考。只从备要。故禫而纯吉者世或有之。然此夫子所谓虽违众。不可从者也。窃观所询。上三段乃父在为母及为本生父母丧之礼。而此一段乃及于二十七月之禫。二十七月之禫。乃丧三年之礼也。此段所论。即丧三年之禫。玆更以十五月已禫者而言之。通典曰心丧已经十五月。祥禫变除。礼毕馀情。一周不应复再禫。心丧之无禫。既有明證。不必多辨也。心丧既无再禫。则二十七月而只有素服。更无可变之服。然丧以二十七月而毕。则哀慕之心。不忍遽吉。而延至于丧毕之月。家礼小祥章曰应服期改吉。然犹尽其月不服金珠红紫。凡诸期丧皆然。况于为其亲心服之丧乎。星湖先生曰心服
于禫而始变其缁。禫而缁则终其月而始就其吉。其间未尝有他变制之服。则从宜而不泥于古。从简而不至于野。后之言礼者。无可改评矣。沙溪所云禫祭服纯吉。终涉可疑。杂记郑注曰禫祭玄衣黄裳。黄裳者未大吉也。间传贾疏曰吉祭以后始从吉。若吉祭在禫月。犹未纯吉。然则禫之纯吉。于古无稽。故家礼禫章亦无吉服之文。则不为纯吉者明矣。沙溪备要禫祭条添入陈吉服三字。又于大祥条释之曰禫祭着吉服。今人丧礼。既未博考。只从备要。故禫而纯吉者世或有之。然此夫子所谓虽违众。不可从者也。窃观所询。上三段乃父在为母及为本生父母丧之礼。而此一段乃及于二十七月之禫。二十七月之禫。乃丧三年之礼也。此段所论。即丧三年之禫。玆更以十五月已禫者而言之。通典曰心丧已经十五月。祥禫变除。礼毕馀情。一周不应复再禫。心丧之无禫。既有明證。不必多辨也。心丧既无再禫。则二十七月而只有素服。更无可变之服。然丧以二十七月而毕。则哀慕之心。不忍遽吉。而延至于丧毕之月。家礼小祥章曰应服期改吉。然犹尽其月不服金珠红紫。凡诸期丧皆然。况于为其亲心服之丧乎。星湖先生曰心服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8L 页
 宜至吉祭之限。变服而晨谒而已。窃意为本生亲者。亦以黪素之服。准此为限。恐合情文耳。礼曰是月禫。徙月乐。即哀杀有渐之义也。
宜至吉祭之限。变服而晨谒而已。窃意为本生亲者。亦以黪素之服。准此为限。恐合情文耳。礼曰是月禫。徙月乐。即哀杀有渐之义也。答申思深(道浚)
俯询礼条。家礼祔章出主条。无告词。盖文略也。未尝无告也。其下云继祖之宗异居则宗子为告于祖。而设虚位以祭。然则虚位之设。既有其告。则奉出置于座。其不可无告者。亦既较然著明也。后之丘氏仪近世备要。亦可谓详悉。而未尝槩及者何也。星湖先生曰以例推之。必无不告之理。当依时祭仪。焚香告词矣。既有先贤之定论。故鄙家亦尝遵用之耳。
与李晋如(济升○甲戌)
日者惠顾。俯询葬礼一节。其时随问随答。槩有酬酢言。而更思之。窃欠其明截。重为覆焉。令第二从氏年既老大。重以摄宗祀十有馀年。大与殇丧异。稽诸礼。虽无后丧之主。祔诸中一以上之庙而祀之。从氏孤儿虽幼。既有子。允哥还承本宗。则又有长从子。主不可不立也。世或有有稚子而无近亲无处室。其身死则丧仪全然不能办。及其稚孤长成。始为之立庙。只缘其势之迫不得已者。而亦委巷之事也。从氏立门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9H 页
 户矣。有妻孥矣。既与彼不得已者。迥然不类。何必取而为例也。古有子生三日。抱衰之礼。故虽襁褓儿。以儿名题主。近世人家所通行者。而子幼不能将事。则祝文及赠玄纁等节。从其服重者允哥摄行。庶乎其可也。古今礼说。未尝分宗支轻重。而历历皆可考也。夫礼者固非一己之私。亦非一人之见。须商确于尊伯氏与佥从氏。又为博访今之知礼家。务归至当。如何如何。前者稚圭丧配时。尝有此变节。知旧中言者间然。尊或闻之否。既有枉询。不可以孤负。玆敢贡愚。恕谅之否。
户矣。有妻孥矣。既与彼不得已者。迥然不类。何必取而为例也。古有子生三日。抱衰之礼。故虽襁褓儿。以儿名题主。近世人家所通行者。而子幼不能将事。则祝文及赠玄纁等节。从其服重者允哥摄行。庶乎其可也。古今礼说。未尝分宗支轻重。而历历皆可考也。夫礼者固非一己之私。亦非一人之见。须商确于尊伯氏与佥从氏。又为博访今之知礼家。务归至当。如何如何。前者稚圭丧配时。尝有此变节。知旧中言者间然。尊或闻之否。既有枉询。不可以孤负。玆敢贡愚。恕谅之否。答郑南一(斗和)
问襄事不得已定以来月。则卒哭退俟礼月之初刚。可以行祀耶。终丁日为可乎。卒哭后祔事。当告由于先庙。而宗家既在绝远。宗孙又在草土。则告由之节。亦难行之。不告于本庙。而自此纸榜行祀。亦涉如何。何以则合于礼耶。
俯询卒哭一节。礼只云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未尝言某日。然礼既曰丧事先远日。盖葬以三月者。虽在上旬。即于三虞后刚日行卒哭。礼之常也。若报葬而待三月则当用远日之礼也。且礼云刚日三虞。
下庐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9L 页
 郑注曰刚阳也。取其动。贾疏曰将祔于祖。取其动义也。况于卒哭祝辞。告以来日隮祔云。则用刚日礼也。然则三月之下旬刚日行祀似可也。祔事告先庙。宗孙虽在丧中。行之似无违礼。若宗孙遭哀则亦自告庙行祔。其在傍亲。宜无异例。若以葬前丧人有嫌。则诸子孙中摄行。亦无不可。苟以宗孙居忧。不敢告庙。则三年之内。诸子孙并不得祔祖。其可乎。幸须博访于知礼家是望。
郑注曰刚阳也。取其动。贾疏曰将祔于祖。取其动义也。况于卒哭祝辞。告以来日隮祔云。则用刚日礼也。然则三月之下旬刚日行祀似可也。祔事告先庙。宗孙虽在丧中。行之似无违礼。若宗孙遭哀则亦自告庙行祔。其在傍亲。宜无异例。若以葬前丧人有嫌。则诸子孙中摄行。亦无不可。苟以宗孙居忧。不敢告庙。则三年之内。诸子孙并不得祔祖。其可乎。幸须博访于知礼家是望。答郑南重(琦和)
方笠古者东俗折风巾之制也。丧服制度皆遵古。故用之。星湖先生云方笠平凉子。俱非礼经所载。出后子哀容无饰。方笠亦无害。前贤之论。既如是矣。然年前知旧中某宰家言礼者。遭本生外丧着方笠。由是是非大作。后之人不识礼之本义。而惟刱见则乃骇。既非当行不可变之礼。则何必违众。惟在哀谅行而已。至若拘于事势。不得守庐。每当月之朝望。设位哭临。是乃至情。虽非古人说到者。亦近于情礼。族亲私亲外党之人。略如吊仪。亦近从宜。哀谕得之。草草奉复。须博访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