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x 页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记
记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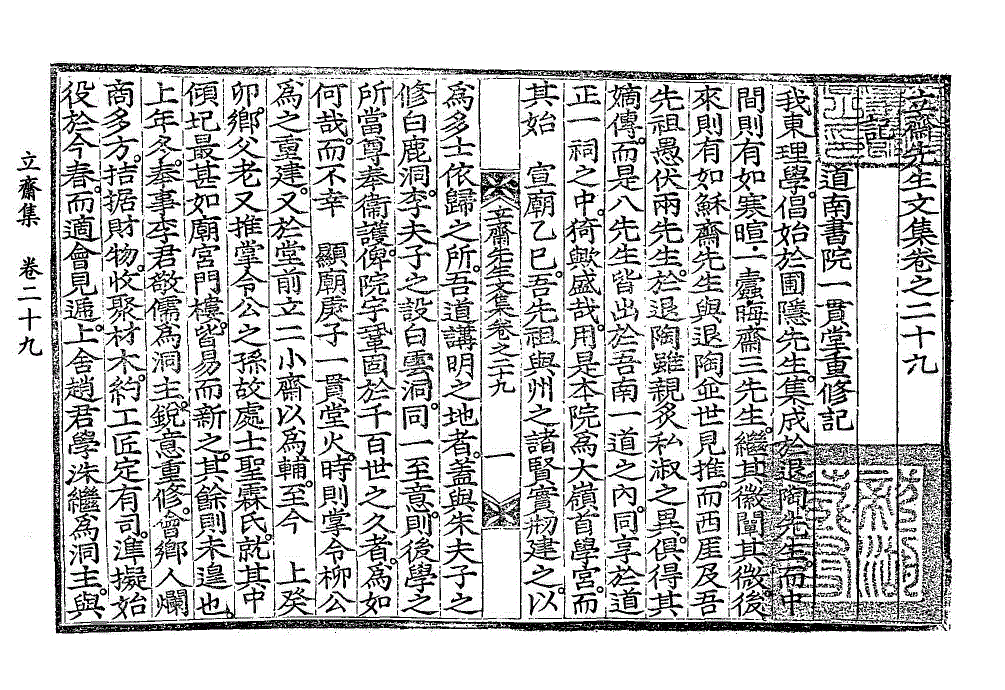 道南书院一贯堂重修记
道南书院一贯堂重修记我东理学。倡始于圃隐先生。集成于退陶先生。而中间则有如寒暄,一蠹,晦斋三先生。继其徽阐其微。后来则有如稣斋先生与退陶并世见推。而西厓及吾先祖愚伏两先生。于退陶虽亲炙私淑之异。俱得其嫡传。而是八先生皆出于吾南一道之内。同享于道正一祠之中。猗欤盛哉。用是本院为大岭首学宫。而其始 宣庙乙巳。吾先祖与州之诸贤实刱建之。以为多士依归之所。吾道讲明之地者。盖与朱夫子之修白鹿洞。李夫子之设白云洞。同一至意。则后学之所当尊奉卫护。俾院宇巩固于千百世之久者。为如何哉。而不幸 显庙庚子一贯堂火。时则掌令柳公为之重建。又于堂前立二小斋以为辅。至今 上癸卯。乡父老又推掌令公之孙故处士圣霖氏。就其中倾圮最甚如庙宫门楼。皆易而新之。其馀则未遑也。上年冬。奉事李君敬儒为洞主。锐意重修。会乡人烂商多方。拮据财物。收聚材木。约工匠定有司。准拟始役于今春。而适会见递。上舍赵君学洙继为洞主。与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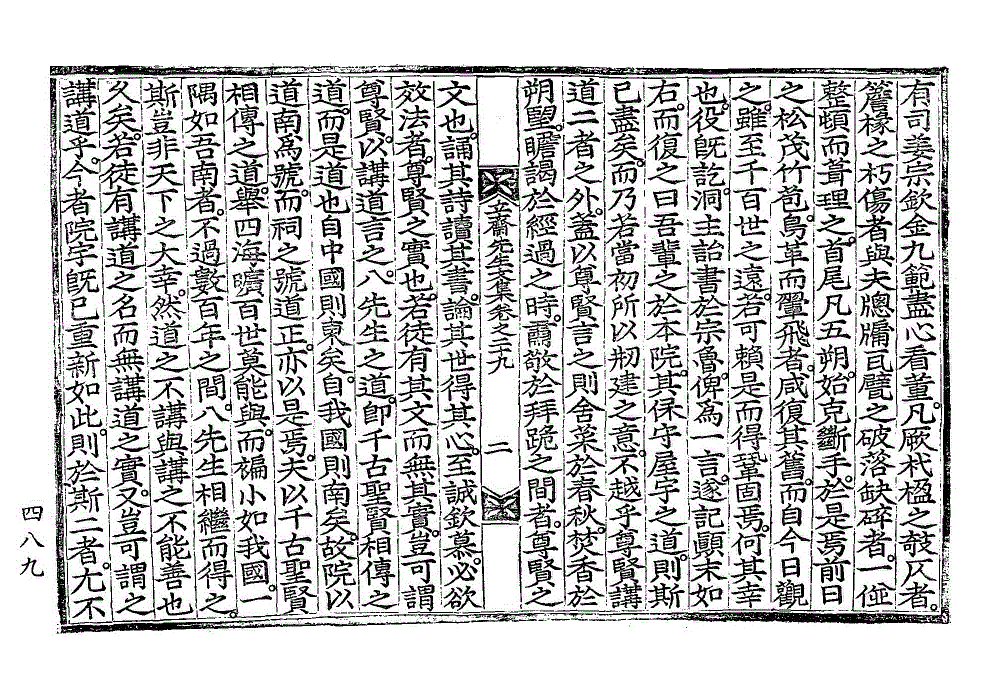 有司姜宗钦,金九范尽心看董。凡厥杙楹之攲仄者。檐椽之朽伤者与夫窗牖瓦甓之破落缺碎者。一并整顿而葺理之。首尾凡五朔。始克断手。于是焉前日之松茂竹苞。鸟革而翚飞者。咸复其旧。而自今日观之。虽至千百世之远。若可赖是而得巩固焉。何其幸也。役既讫。洞主诒书于宗鲁。俾为一言。遂记颠末如右。而复之曰吾辈之于本院。其保守屋宇之道。则斯已尽矣。而乃若当初所以刱建之意。不越乎尊贤讲道二者之外。盖以尊贤言之则舍菜于春秋。焚香于朔望。瞻谒于经过之时。肃敬于拜跪之间者。尊贤之文也。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得其心。至诚钦慕。必欲效法者。尊贤之实也。若徒有其文而无其实。岂可谓尊贤。以讲道言之。八先生之道。即千古圣贤相传之道。而是道也自中国则东矣。自我国则南矣。故院以道南为号。而祠之号道正。亦以是焉。夫以千古圣贤相传之道。举四海旷百世莫能与。而褊小如我国。一隅如吾南者。不过数百年之间。八先生相继而得之。斯岂非天下之大幸。然道之不讲与讲之不能善也久矣。若徒有讲道之名而无讲道之实。又岂可谓之讲道乎。今者院宇既已重新如此。则于斯二者。尤不
有司姜宗钦,金九范尽心看董。凡厥杙楹之攲仄者。檐椽之朽伤者与夫窗牖瓦甓之破落缺碎者。一并整顿而葺理之。首尾凡五朔。始克断手。于是焉前日之松茂竹苞。鸟革而翚飞者。咸复其旧。而自今日观之。虽至千百世之远。若可赖是而得巩固焉。何其幸也。役既讫。洞主诒书于宗鲁。俾为一言。遂记颠末如右。而复之曰吾辈之于本院。其保守屋宇之道。则斯已尽矣。而乃若当初所以刱建之意。不越乎尊贤讲道二者之外。盖以尊贤言之则舍菜于春秋。焚香于朔望。瞻谒于经过之时。肃敬于拜跪之间者。尊贤之文也。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得其心。至诚钦慕。必欲效法者。尊贤之实也。若徒有其文而无其实。岂可谓尊贤。以讲道言之。八先生之道。即千古圣贤相传之道。而是道也自中国则东矣。自我国则南矣。故院以道南为号。而祠之号道正。亦以是焉。夫以千古圣贤相传之道。举四海旷百世莫能与。而褊小如我国。一隅如吾南者。不过数百年之间。八先生相继而得之。斯岂非天下之大幸。然道之不讲与讲之不能善也久矣。若徒有讲道之名而无讲道之实。又岂可谓之讲道乎。今者院宇既已重新如此。则于斯二者。尤不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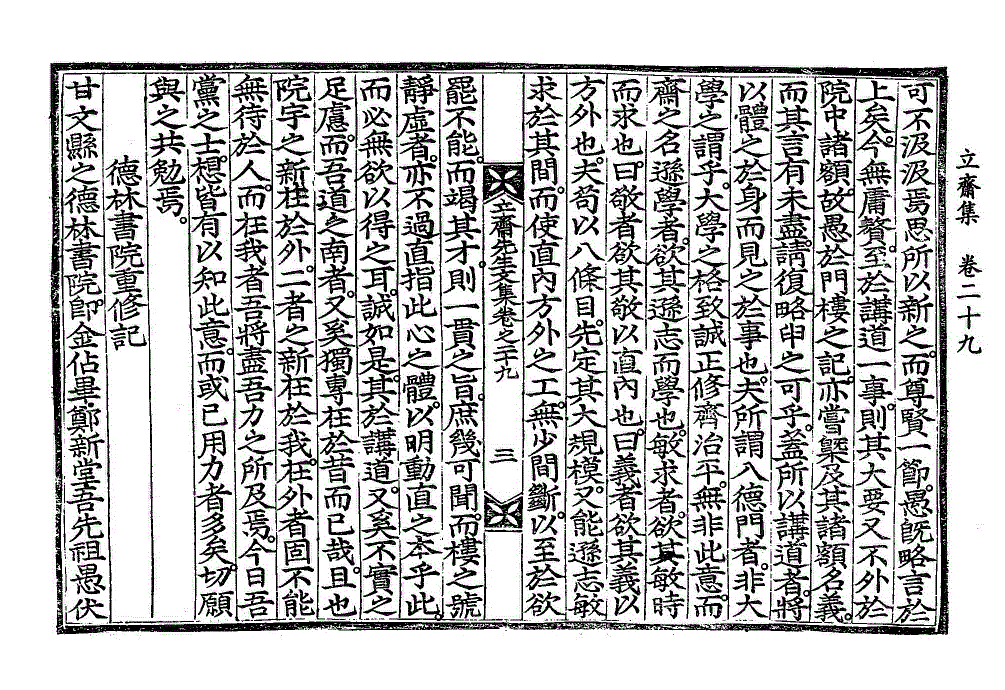 可不汲汲焉思所以新之。而尊贤一节。愚既略言于上矣。今无庸赘。至于讲道一事。则其大要又不外于院中诸额。故愚于门楼之记。亦尝槩及其诸额名义。而其言有未尽。请复略申之可乎。盖所以讲道者。将以体之于身而见之于事也。夫所谓入德门者。非大学之谓乎。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无非此意。而斋之名逊学者。欲其逊志而学也。敏求者。欲其敏时而求也。曰敬者欲其敬以直内也。曰义者欲其义以方外也。夫苟以八条目。先定其大规模。又能逊志敏求于其间。而使直内方外之工。无少间断。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一贯之旨。庶几可闻。而楼之号静虚者。亦不过直指此心之体。以明动直之本乎此。而必无欲以得之耳。诚如是。其于讲道。又奚不实之足虑。而吾道之南者。又奚独专在于昔而已哉。且也院宇之新在于外。二者之新在于我。在外者固不能无待于人。而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及焉。今日吾党之士。想皆有以知此意。而或已用力者多矣。切愿与之共勉焉。
可不汲汲焉思所以新之。而尊贤一节。愚既略言于上矣。今无庸赘。至于讲道一事。则其大要又不外于院中诸额。故愚于门楼之记。亦尝槩及其诸额名义。而其言有未尽。请复略申之可乎。盖所以讲道者。将以体之于身而见之于事也。夫所谓入德门者。非大学之谓乎。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无非此意。而斋之名逊学者。欲其逊志而学也。敏求者。欲其敏时而求也。曰敬者欲其敬以直内也。曰义者欲其义以方外也。夫苟以八条目。先定其大规模。又能逊志敏求于其间。而使直内方外之工。无少间断。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一贯之旨。庶几可闻。而楼之号静虚者。亦不过直指此心之体。以明动直之本乎此。而必无欲以得之耳。诚如是。其于讲道。又奚不实之足虑。而吾道之南者。又奚独专在于昔而已哉。且也院宇之新在于外。二者之新在于我。在外者固不能无待于人。而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及焉。今日吾党之士。想皆有以知此意。而或已用力者多矣。切愿与之共勉焉。德林书院重修记
甘文县之德林书院。即金佔毕,郑新堂,吾先祖愚伏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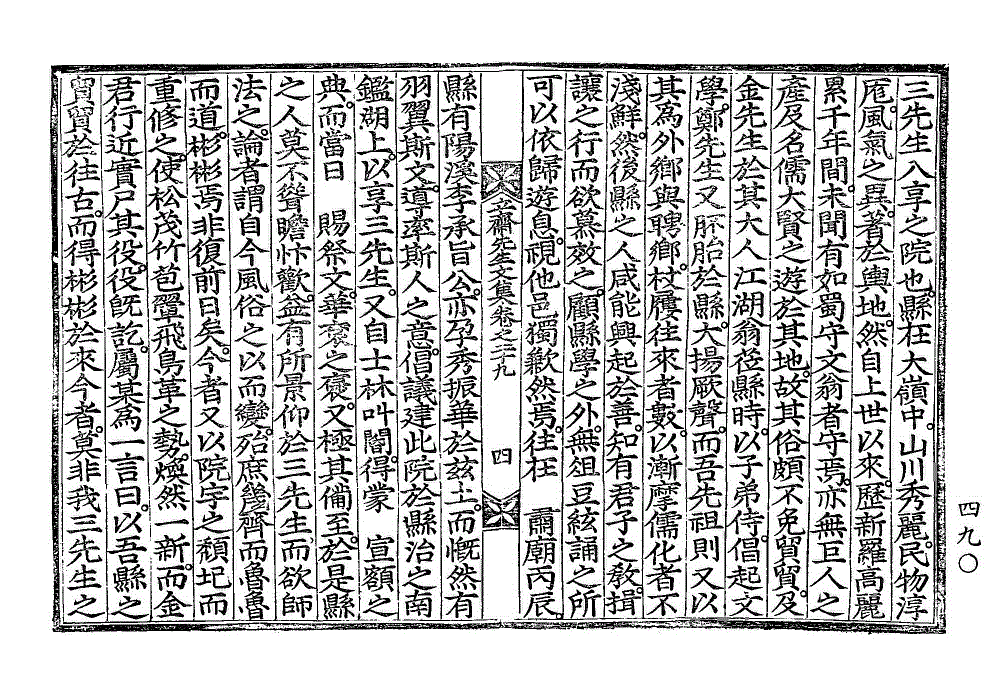 三先生入享之院也。县在大岭中。山川秀丽。民物淳厖。风气之异。著于舆地。然自上世以来。历新罗高丽累千年间。未闻有如蜀守文翁者守焉。亦无巨人之产及名儒大贤之游于其地。故其俗颇不免贸贸。及金先生于其大人江湖翁莅县时。以子弟侍。倡起文学。郑先生又胚胎于县。大扬厥声。而吾先祖则又以其为外乡与聘乡。杖屦往来者数。以渐摩儒化者不浅鲜。然后县之人咸能兴起于善。知有君子之教。揖让之行而欲慕效之。顾县学之外。无俎豆弦诵之所可以依归游息。视他邑独歉然焉。往在 肃庙丙辰。县有阳溪李承旨公。亦孕秀振华于玆土。而慨然有羽翼斯文。导率斯人之意。倡议建此院于县治之南鉴湖上。以享三先生。又自士林叫阍。得蒙 宣额之典。而当日 赐祭文。华衮之褒。又极其备至。于是县之人莫不耸瞻忭欢。益有所景仰于三先生。而欲师法之。论者谓自今风俗之以而变。殆庶几齐而鲁鲁而道。彬彬焉非复前日矣。今者又以院宇之颓圮而重修之。使松茂竹苞翚飞鸟革之势。焕然一新。而金君行近实尸其役。役既讫。属某为一言曰。以吾县之贸贸于往古。而得彬彬于来今者。莫非我三先生之
三先生入享之院也。县在大岭中。山川秀丽。民物淳厖。风气之异。著于舆地。然自上世以来。历新罗高丽累千年间。未闻有如蜀守文翁者守焉。亦无巨人之产及名儒大贤之游于其地。故其俗颇不免贸贸。及金先生于其大人江湖翁莅县时。以子弟侍。倡起文学。郑先生又胚胎于县。大扬厥声。而吾先祖则又以其为外乡与聘乡。杖屦往来者数。以渐摩儒化者不浅鲜。然后县之人咸能兴起于善。知有君子之教。揖让之行而欲慕效之。顾县学之外。无俎豆弦诵之所可以依归游息。视他邑独歉然焉。往在 肃庙丙辰。县有阳溪李承旨公。亦孕秀振华于玆土。而慨然有羽翼斯文。导率斯人之意。倡议建此院于县治之南鉴湖上。以享三先生。又自士林叫阍。得蒙 宣额之典。而当日 赐祭文。华衮之褒。又极其备至。于是县之人莫不耸瞻忭欢。益有所景仰于三先生。而欲师法之。论者谓自今风俗之以而变。殆庶几齐而鲁鲁而道。彬彬焉非复前日矣。今者又以院宇之颓圮而重修之。使松茂竹苞翚飞鸟革之势。焕然一新。而金君行近实尸其役。役既讫。属某为一言曰。以吾县之贸贸于往古。而得彬彬于来今者。莫非我三先生之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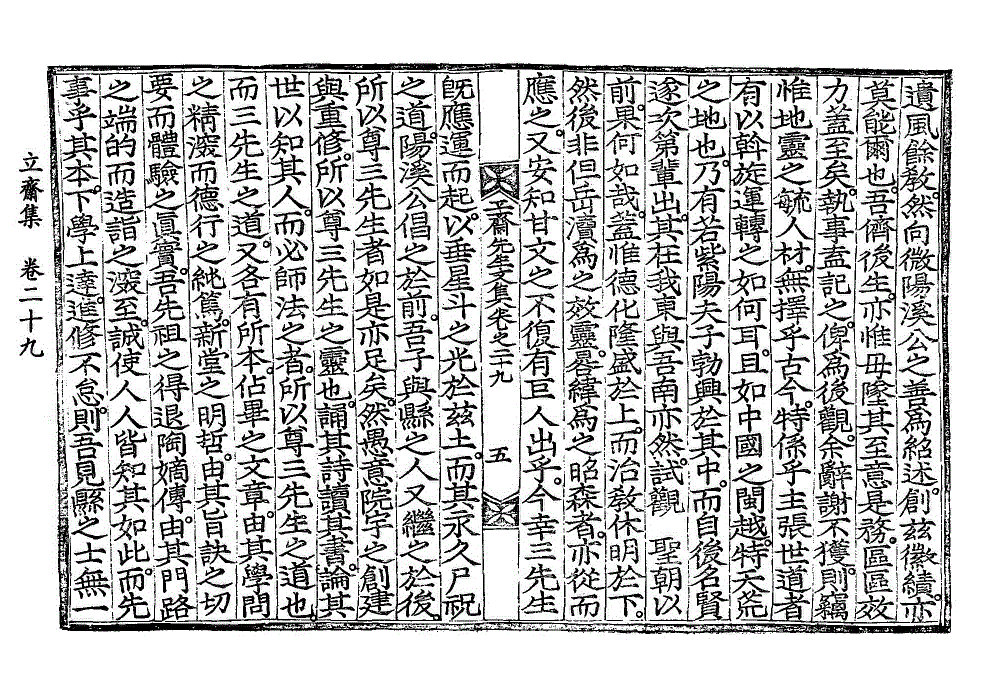 遗风馀教。然向微阳溪公之善为绍述。创玆徽绩。亦莫能尔也。吾侪后生。亦惟毋坠其至意是务。区区效力盖至矣。执事盍记之。俾为后观。余辞谢不获。则窃惟地灵之毓人材。无择乎古今。特系乎主张世道者有以斡旋运转之如何耳。且如中国之闽越。特天荒之地也。乃有若紫阳夫子勃兴于其中。而自后名贤遂次第辈出。其在我东与吾南亦然。试观 圣朝以前。果何如哉。盖惟德化隆盛于上。而治教休明于下。然后非但岳渎为之效灵。晷纬为之昭森者。亦从而应之。又安知甘文之不复有巨人出乎。今幸三先生既应运而起。以垂星斗之光于玆土。而其永久尸祝之道。阳溪公倡之于前。吾子与县之人又继之于后。所以尊三先生者如是亦足矣。然愚意院宇之创建与重修。所以尊三先生之灵也。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以知其人。而必师法之者。所以尊三先生之道也。而三先生之道。又各有所本。佔毕之文章。由其学问之精深而德行之纯笃。新堂之明哲。由其旨诀之切要而体验之真实。吾先祖之得退陶嫡传。由其门路之端的而造诣之深至。诚使人人皆知其如此。而先事乎其本。下学上达。进修不怠。则吾见县之士无一
遗风馀教。然向微阳溪公之善为绍述。创玆徽绩。亦莫能尔也。吾侪后生。亦惟毋坠其至意是务。区区效力盖至矣。执事盍记之。俾为后观。余辞谢不获。则窃惟地灵之毓人材。无择乎古今。特系乎主张世道者有以斡旋运转之如何耳。且如中国之闽越。特天荒之地也。乃有若紫阳夫子勃兴于其中。而自后名贤遂次第辈出。其在我东与吾南亦然。试观 圣朝以前。果何如哉。盖惟德化隆盛于上。而治教休明于下。然后非但岳渎为之效灵。晷纬为之昭森者。亦从而应之。又安知甘文之不复有巨人出乎。今幸三先生既应运而起。以垂星斗之光于玆土。而其永久尸祝之道。阳溪公倡之于前。吾子与县之人又继之于后。所以尊三先生者如是亦足矣。然愚意院宇之创建与重修。所以尊三先生之灵也。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以知其人。而必师法之者。所以尊三先生之道也。而三先生之道。又各有所本。佔毕之文章。由其学问之精深而德行之纯笃。新堂之明哲。由其旨诀之切要而体验之真实。吾先祖之得退陶嫡传。由其门路之端的而造诣之深至。诚使人人皆知其如此。而先事乎其本。下学上达。进修不怠。则吾见县之士无一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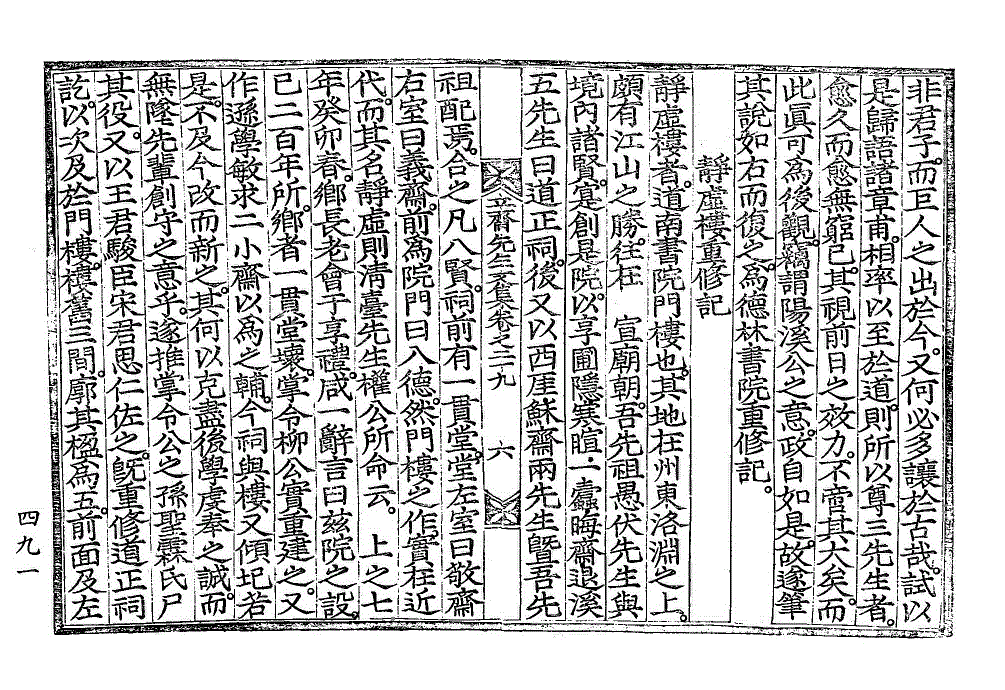 非君子。而巨人之出于今。又何必多让于古哉。试以是归语诸章甫。相率以至于道。则所以尊三先生者。愈久而愈无穷已。其视前日之效力。不啻其大矣。而此真可为后观。窃谓阳溪公之意。政自如是。故遂笔其说如右而复之。为德林书院重修记。
非君子。而巨人之出于今。又何必多让于古哉。试以是归语诸章甫。相率以至于道。则所以尊三先生者。愈久而愈无穷已。其视前日之效力。不啻其大矣。而此真可为后观。窃谓阳溪公之意。政自如是。故遂笔其说如右而复之。为德林书院重修记。静虚楼重修记
静虚楼者。道南书院门楼也。其地在州东洛渊之上。颇有江山之胜。往在 宣庙朝。吾先祖愚伏先生与境内诸贤。寔创是院。以享圃隐,寒暄,一蠹,晦斋,退溪五先生曰道正祠。后又以西厓,稣斋两先生暨吾先祖配焉。合之凡八贤。祠前有一贯堂。堂左室曰敬斋右室曰义斋。前为院门曰入德。然门楼之作。实在近代。而其名静虚则清台先生权公所命云。 上之七年癸卯春。乡长老会于享礼。咸一辞言曰玆院之设。已二百年所。乡者一贯堂坏。掌令柳公实重建之。又作逊学敏求二小斋以为之辅。今祠与楼又倾圮若是。不及今改而新之。其何以克尽后学虔奉之诚。而无坠先辈创守之意乎。遂推掌令公之孙圣霖氏尸其役。又以王君骏臣宋君思仁佐之。既重修道正祠讫。以次及于门楼。楼旧三间。廓其楹为五。前面及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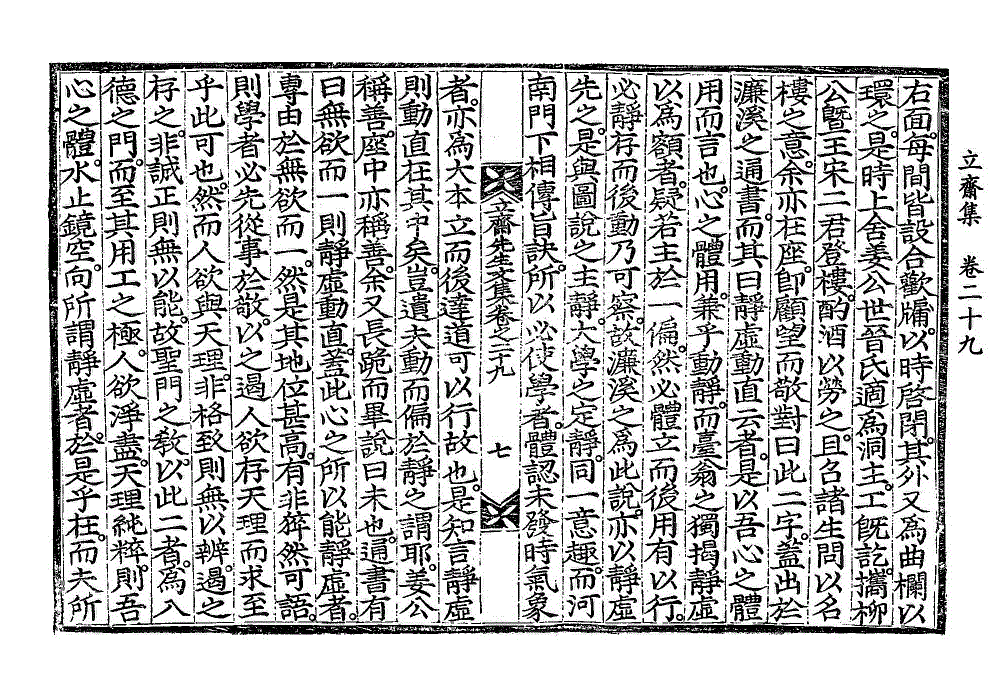 右面。每间皆设合欢牖。以时启闭。其外又为曲栏以环之。是时上舍姜公世晋氏适为洞主。工既讫。携柳公暨王宋二君登楼。酌酒以劳之。且召诸生问以名楼之意。余亦在座。即顾望而敬对曰此二字。盖出于濂溪之通书。而其曰静虚动直云者。是以吾心之体用而言也。心之体用。兼乎动静。而台翁之独揭静虚以为额者。疑若主于一偏。然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必静存而后动乃可察。故濂溪之为此说。亦以静虚先之。是与图说之主静。大学之定静。同一意趣。而河南门下相传旨诀。所以必使学者。体认未发时气象者。亦为大本立而后达道可以行故也。是知言静虚则动直在其中矣。岂遗夫动而偏于静之谓耶。姜公称善。座中亦称善。余又长跪而毕说曰未也。通书有曰无欲而一则静虚动直。盖此心之所以能静虚者。专由于无欲而一。然是其地位甚高。有非猝然可语。则学者必先从事于敬。以之遏人欲存天理而求至乎此可也。然而人欲与天理。非格致则无以辨。遏之存之。非诚正则无以能。故圣门之教。以此二者。为入德之门。而至其用工之极。人欲净尽。天理纯粹。则吾心之体。水止镜空。向所谓静虚者。于是乎在。而夫所
右面。每间皆设合欢牖。以时启闭。其外又为曲栏以环之。是时上舍姜公世晋氏适为洞主。工既讫。携柳公暨王宋二君登楼。酌酒以劳之。且召诸生问以名楼之意。余亦在座。即顾望而敬对曰此二字。盖出于濂溪之通书。而其曰静虚动直云者。是以吾心之体用而言也。心之体用。兼乎动静。而台翁之独揭静虚以为额者。疑若主于一偏。然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必静存而后动乃可察。故濂溪之为此说。亦以静虚先之。是与图说之主静。大学之定静。同一意趣。而河南门下相传旨诀。所以必使学者。体认未发时气象者。亦为大本立而后达道可以行故也。是知言静虚则动直在其中矣。岂遗夫动而偏于静之谓耶。姜公称善。座中亦称善。余又长跪而毕说曰未也。通书有曰无欲而一则静虚动直。盖此心之所以能静虚者。专由于无欲而一。然是其地位甚高。有非猝然可语。则学者必先从事于敬。以之遏人欲存天理而求至乎此可也。然而人欲与天理。非格致则无以辨。遏之存之。非诚正则无以能。故圣门之教。以此二者。为入德之门。而至其用工之极。人欲净尽。天理纯粹。则吾心之体。水止镜空。向所谓静虚者。于是乎在。而夫所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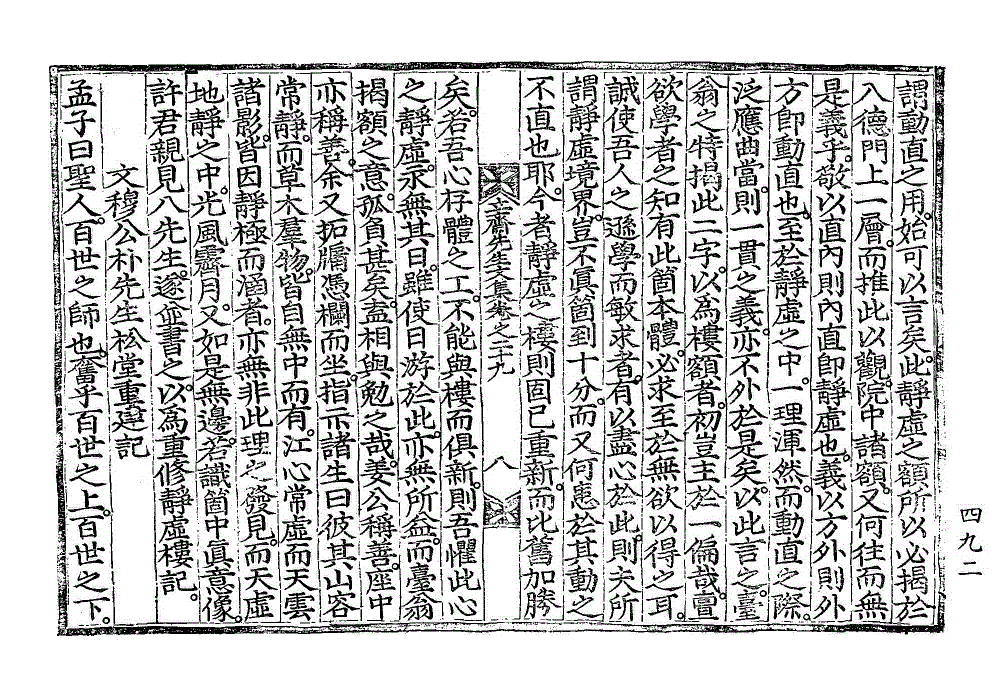 谓动直之用。始可以言矣。此静虚之额所以必揭于入德门上一层。而推此以观。院中诸额。又何往而无是义乎。敬以直内则内直即静虚也。义以方外则外方即动直也。至于静虚之中。一理浑然。而动直之际。泛应曲当。则一贯之义。亦不外于是矣。以此言之。台翁之特揭此二字。以为楼额者。初岂主于一偏哉。亶欲学者之知有此个本体。必求至于无欲以得之耳。诚使吾人之逊学而敏求者。有以尽心于此。则夫所谓静虚境界。岂不真个到十分。而又何患于其动之不直也耶。今者静虚之楼则固已重新。而比旧加胜矣。若吾心存体之工。不能与楼而俱新。则吾惧此心之静虚。永无其日。虽使日游于此。亦无所益。而台翁揭额之意。孤负甚矣。盍相与勉之哉。姜公称善。座中亦称善。余又拓牖凭栏而坐。指示诸生曰彼其山容常静。而草木群物。皆自无中而有。江心常虚而天云诸影。皆因静极而涵者。亦无非此理之发见。而天虚地静之中。光风霁月。又如是无边。若识个中真意像。许君亲见八先生。遂并书之。以为重修静虚楼记。
谓动直之用。始可以言矣。此静虚之额所以必揭于入德门上一层。而推此以观。院中诸额。又何往而无是义乎。敬以直内则内直即静虚也。义以方外则外方即动直也。至于静虚之中。一理浑然。而动直之际。泛应曲当。则一贯之义。亦不外于是矣。以此言之。台翁之特揭此二字。以为楼额者。初岂主于一偏哉。亶欲学者之知有此个本体。必求至于无欲以得之耳。诚使吾人之逊学而敏求者。有以尽心于此。则夫所谓静虚境界。岂不真个到十分。而又何患于其动之不直也耶。今者静虚之楼则固已重新。而比旧加胜矣。若吾心存体之工。不能与楼而俱新。则吾惧此心之静虚。永无其日。虽使日游于此。亦无所益。而台翁揭额之意。孤负甚矣。盍相与勉之哉。姜公称善。座中亦称善。余又拓牖凭栏而坐。指示诸生曰彼其山容常静。而草木群物。皆自无中而有。江心常虚而天云诸影。皆因静极而涵者。亦无非此理之发见。而天虚地静之中。光风霁月。又如是无边。若识个中真意像。许君亲见八先生。遂并书之。以为重修静虚楼记。文穆公朴先生松堂重建记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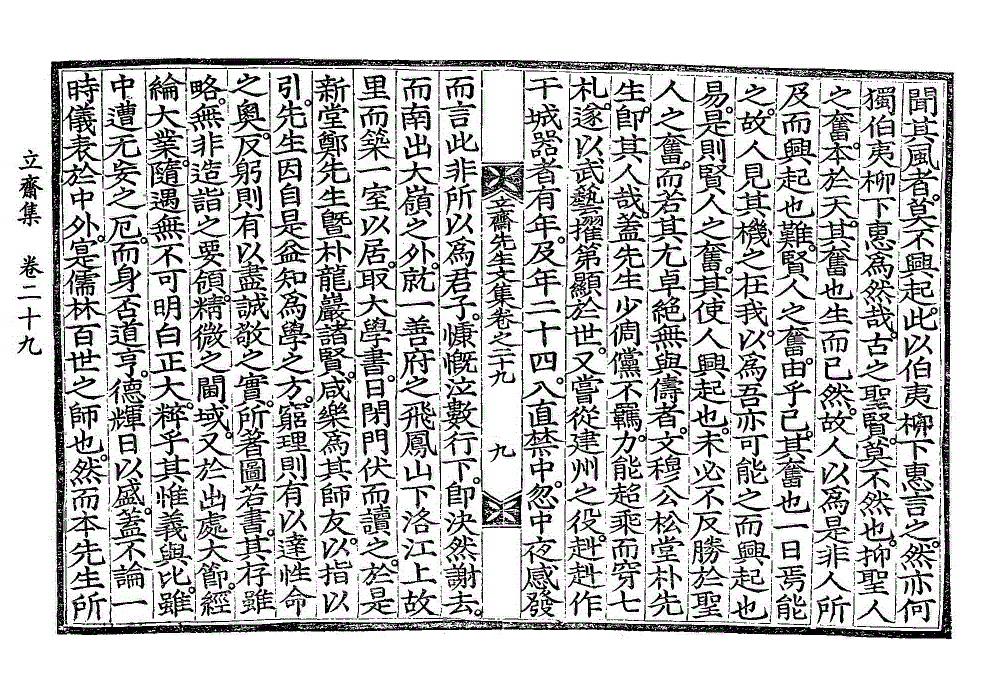 闻其风者。莫不兴起。此以伯夷柳下惠言之。然亦何独伯夷柳下惠为然哉。古之圣贤。莫不然也。抑圣人之奋。本于天。其奋也生而已然。故人以为是非人所及而兴起也难。贤人之奋。由乎已。其奋也一日焉能之。故人见其机之在我。以为吾亦可能之而兴起也易。是则贤人之奋。其使人兴起也。未必不反胜于圣人之奋。而若其尤卓绝无与俦者。文穆公松堂朴先生。即其人哉。盖先生少倜傥不羁。力能超乘而穿七札。遂以武艺擢第显于世。又尝从建州之役。赳赳作干城器者有年。及年二十四。入直禁中。忽中夜感发而言此非所以为君子。慷慨泣数行下。即决然谢去。而南出大岭之外。就一善府之飞凤山下洛江上故里而筑一室以居。取大学书。日闭门伏而读之。于是新堂郑先生暨朴龙岩诸贤。咸乐为其师友。以指以引。先生因自是益知为学之方。穷理则有以达性命之奥。反躬则有以尽诚敬之实。所著图若书。其存虽略。无非造诣之要领。精微之阃域。又于出处大节。经纶大业。随遇无不可明白正大。粹乎其惟义与比。虽中遭无妄之厄。而身否道亨。德辉日以盛。盖不论一时仪表于中外。寔儒林百世之师也。然而本先生所
闻其风者。莫不兴起。此以伯夷柳下惠言之。然亦何独伯夷柳下惠为然哉。古之圣贤。莫不然也。抑圣人之奋。本于天。其奋也生而已然。故人以为是非人所及而兴起也难。贤人之奋。由乎已。其奋也一日焉能之。故人见其机之在我。以为吾亦可能之而兴起也易。是则贤人之奋。其使人兴起也。未必不反胜于圣人之奋。而若其尤卓绝无与俦者。文穆公松堂朴先生。即其人哉。盖先生少倜傥不羁。力能超乘而穿七札。遂以武艺擢第显于世。又尝从建州之役。赳赳作干城器者有年。及年二十四。入直禁中。忽中夜感发而言此非所以为君子。慷慨泣数行下。即决然谢去。而南出大岭之外。就一善府之飞凤山下洛江上故里而筑一室以居。取大学书。日闭门伏而读之。于是新堂郑先生暨朴龙岩诸贤。咸乐为其师友。以指以引。先生因自是益知为学之方。穷理则有以达性命之奥。反躬则有以尽诚敬之实。所著图若书。其存虽略。无非造诣之要领。精微之阃域。又于出处大节。经纶大业。随遇无不可明白正大。粹乎其惟义与比。虽中遭无妄之厄。而身否道亨。德辉日以盛。盖不论一时仪表于中外。寔儒林百世之师也。然而本先生所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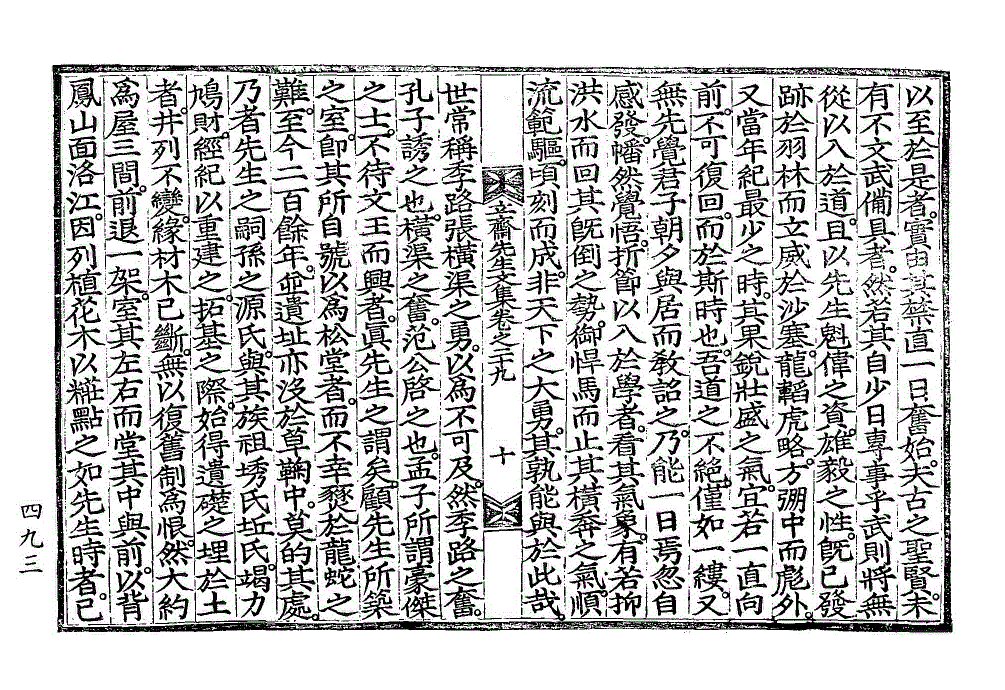 以至于是者。实由其禁直一日奋始。夫古之圣贤。未有不文武备具者。然若其自少日专事乎武则将无从以入于道。且以先生魁伟之资。雄毅之性。既已发迹于羽林而立威于沙塞。龙韬虎略。方弸中而彪外。又当年纪最少之时。其果锐壮盛之气。宜若一直向前。不可复回。而于斯时也。吾道之不绝。仅如一缕。又无先觉君子朝夕与居而教诏之。乃能一日焉忽自感发。幡然觉悟。折节以入于学者。看其气象。有若抑洪水而回其既倒之势。御悍马而止其横奔之气。顺流范驱。顷刻而成。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此哉。世常称季路张横渠之勇。以为不可及。然季路之奋。孔子诱之也。横渠之奋。范公启之也。孟子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真先生之谓矣。顾先生所筑之室。即其所自号以为松堂者。而不幸燹于龙蛇之难。至今二百馀年。并遗址亦没于草鞠中。莫的其处。乃者先生之嗣孙之源氏。与其族祖𪣜氏丘氏。竭力鸠财。经纪以重建之。拓基之际。始得遗础之埋于土者。井列不变。缘材木已断。无以复旧制为恨。然大约为屋三间。前退一架。室其左右而堂其中与前。以背凤山面洛江。因列植花木以妆点之如先生时者。已
以至于是者。实由其禁直一日奋始。夫古之圣贤。未有不文武备具者。然若其自少日专事乎武则将无从以入于道。且以先生魁伟之资。雄毅之性。既已发迹于羽林而立威于沙塞。龙韬虎略。方弸中而彪外。又当年纪最少之时。其果锐壮盛之气。宜若一直向前。不可复回。而于斯时也。吾道之不绝。仅如一缕。又无先觉君子朝夕与居而教诏之。乃能一日焉忽自感发。幡然觉悟。折节以入于学者。看其气象。有若抑洪水而回其既倒之势。御悍马而止其横奔之气。顺流范驱。顷刻而成。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此哉。世常称季路张横渠之勇。以为不可及。然季路之奋。孔子诱之也。横渠之奋。范公启之也。孟子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真先生之谓矣。顾先生所筑之室。即其所自号以为松堂者。而不幸燹于龙蛇之难。至今二百馀年。并遗址亦没于草鞠中。莫的其处。乃者先生之嗣孙之源氏。与其族祖𪣜氏丘氏。竭力鸠财。经纪以重建之。拓基之际。始得遗础之埋于土者。井列不变。缘材木已断。无以复旧制为恨。然大约为屋三间。前退一架。室其左右而堂其中与前。以背凤山面洛江。因列植花木以妆点之如先生时者。已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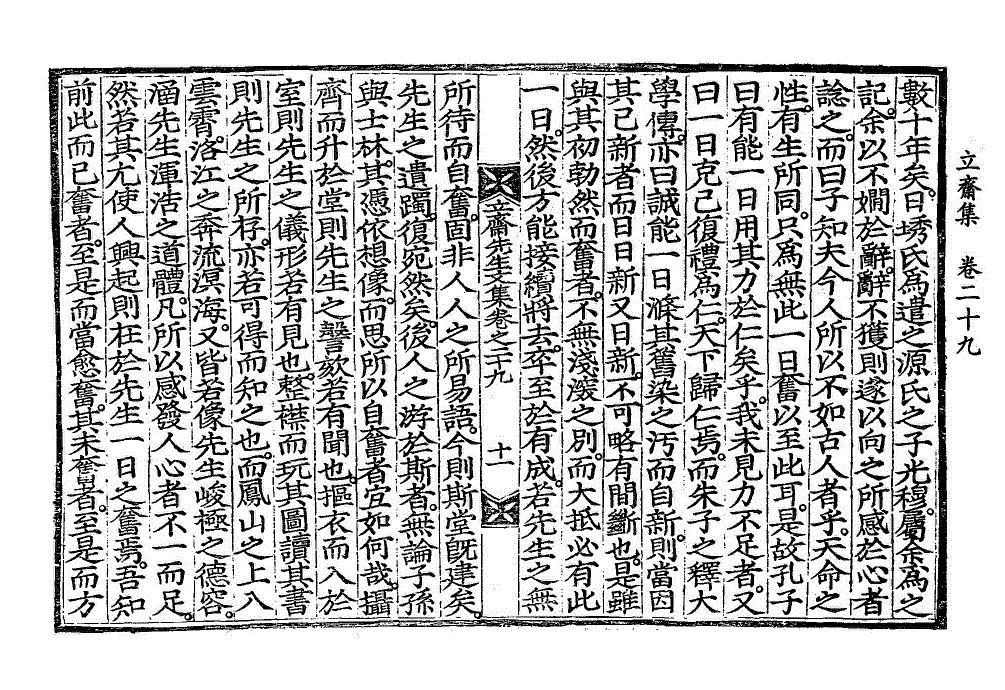 数十年矣。日𪣜氏为遣之源氏之子光穆。属余为之记。余以不娴于辞。辞不获则遂以向之所感于心者谂之。而曰子知夫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乎。天命之性。有生所同。只为无此一日奋以至此耳。是故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曰一日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焉。而朱子之释大学传。亦曰诚能一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又日新。不可略有间断也。是虽与其初勃然而奋者。不无浅深之别。而大抵必有此一日。然后方能接续将去。卒至于有成。若先生之无所待而自奋。固非人人之所易语。今则斯堂既建矣。先生之遗躅。复宛然矣。后人之游于斯者。无论子孙与士林。其凭依想像。而思所以自奋者宜如何哉。摄齐而升于堂则先生之謦欬若有闻也。抠衣而入于室则先生之仪形若有见也。整襟而玩其图读其书则先生之所存。亦若可得而知之也。而凤山之上入云霄。洛江之奔流溟海。又皆若像先生峻极之德容。涵先生浑浩之道体。凡所以感发人心者不一而足。然若其尤使人兴起则在于先生一日之奋焉。吾知前此而已奋者。至是而当愈奋。其未奋者。至是而方
数十年矣。日𪣜氏为遣之源氏之子光穆。属余为之记。余以不娴于辞。辞不获则遂以向之所感于心者谂之。而曰子知夫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乎。天命之性。有生所同。只为无此一日奋以至此耳。是故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曰一日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焉。而朱子之释大学传。亦曰诚能一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又日新。不可略有间断也。是虽与其初勃然而奋者。不无浅深之别。而大抵必有此一日。然后方能接续将去。卒至于有成。若先生之无所待而自奋。固非人人之所易语。今则斯堂既建矣。先生之遗躅。复宛然矣。后人之游于斯者。无论子孙与士林。其凭依想像。而思所以自奋者宜如何哉。摄齐而升于堂则先生之謦欬若有闻也。抠衣而入于室则先生之仪形若有见也。整襟而玩其图读其书则先生之所存。亦若可得而知之也。而凤山之上入云霄。洛江之奔流溟海。又皆若像先生峻极之德容。涵先生浑浩之道体。凡所以感发人心者不一而足。然若其尤使人兴起则在于先生一日之奋焉。吾知前此而已奋者。至是而当愈奋。其未奋者。至是而方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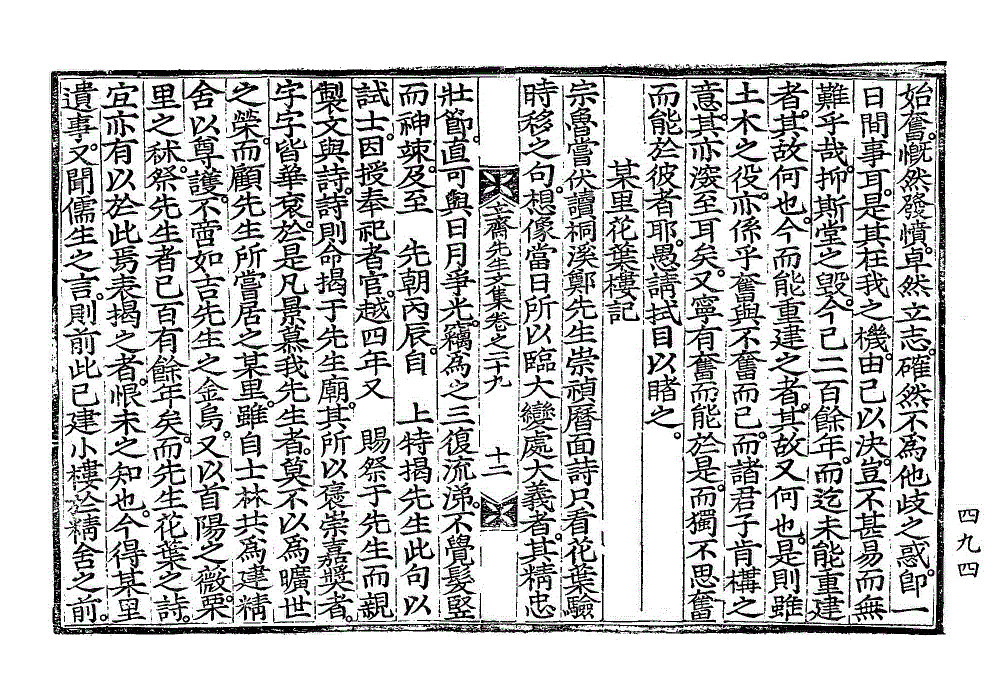 始奋。慨然发愤。卓然立志。确然不为他歧之惑。即一日间事耳。是其在我之机。由己以决。岂不甚易而无难乎哉。抑斯堂之毁。今已二百馀年。而迄未能重建者。其故何也。今而能重建之者。其故又何也。是则虽土木之役。亦系乎奋与不奋而已。而诸君子肯构之意。其亦深至耳矣。又宁有奋而能于是。而独不思奋而能于彼者耶。愚请拭目以睹之。
始奋。慨然发愤。卓然立志。确然不为他歧之惑。即一日间事耳。是其在我之机。由己以决。岂不甚易而无难乎哉。抑斯堂之毁。今已二百馀年。而迄未能重建者。其故何也。今而能重建之者。其故又何也。是则虽土木之役。亦系乎奋与不奋而已。而诸君子肯构之意。其亦深至耳矣。又宁有奋而能于是。而独不思奋而能于彼者耶。愚请拭目以睹之。某里花叶楼记
宗鲁尝伏读桐溪郑先生崇祯历面诗只看花叶验时移之句。想像当日所以临大变处大义者。其精忠壮节。直可与日月争光。窃为之三复流涕。不觉发竖而神竦。及至 先朝丙辰。自 上特揭先生此句以试士。因授奉祀者官。越四年又 赐祭于先生而亲制文与诗。诗则命揭于先生庙。其所以褒崇嘉奖者。字字皆华衮。于是凡景慕我先生者。莫不以为旷世之荣。而顾先生所尝居之某里。虽自士林共为建精舍以尊护。不啻如吉先生之金乌。又以首阳之薇。栗里之秫。祭先生者已百有馀年矣。而先生花叶之诗。宜亦有以于此焉表揭之者。恨未之知也。今得某里遗事。又闻儒生之言。则前此已建小楼于精舍之前。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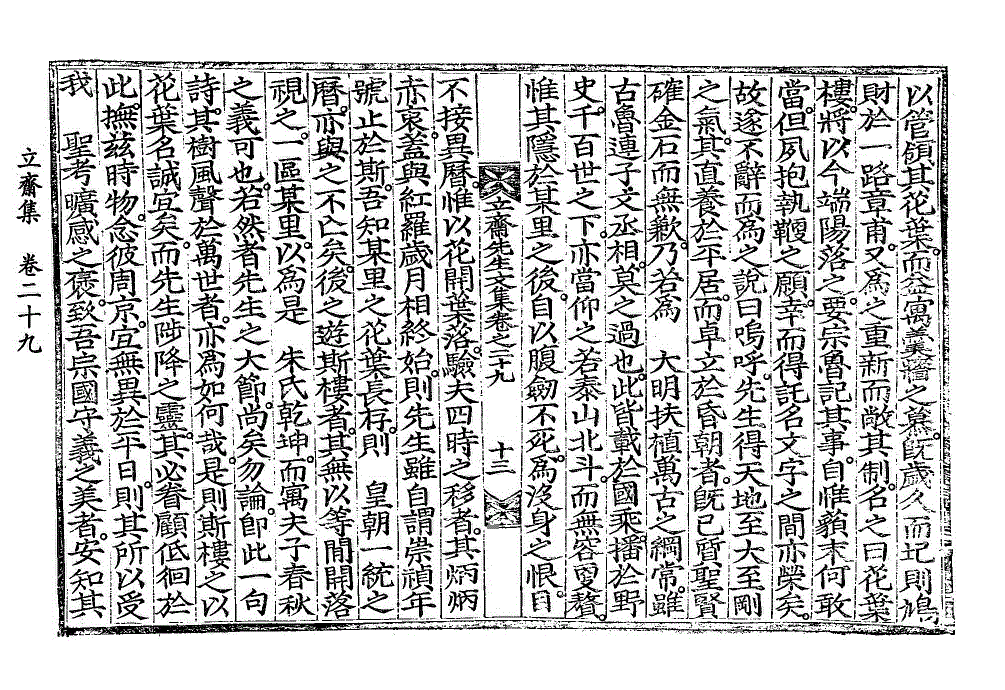 以管领其花叶。而益寓羹墙之慕。既岁久而圮则鸠财于一路章甫。又为之重新而敞其制。名之曰花叶楼。将以今端阳落之。要宗鲁记其事。自惟藐末何敢当。但夙抱执鞭之愿。幸而得托名文字之间亦荣矣。故遂不辞而为之说曰呜呼。先生得天地至大至刚之气。其直养于平居。而卓立于昏朝者。既已质圣贤确金石而无歉。乃若为 大明扶植万古之纲常。虽古鲁连子,文丞相。莫之过也。此皆载于国乘。播于野史。千百世之下。亦当仰之若泰山北斗。而无容更赘。惟其隐于某里之后。自以腹剑不死。为没身之恨。目不接异历。惟以花开叶落。验夫四时之移者。其炳炳赤衷。盖与红罗岁月相终始。则先生虽自谓崇祯年号止于斯。吾知某里之花叶长存。则 皇朝一统之历。亦与之不亡矣。后之游斯楼者。其无以等閒开落视之。一区某里。以为是 朱氏乾坤。而寓夫子春秋之义可也。若然者先生之大节。尚矣勿论。即此一句诗。其树风声于万世者。亦为如何哉。是则斯楼之以花叶名诚宜矣。而先生陟降之灵。其必眷顾低徊于此。抚玆时物。念彼周京。宜无异于平日。则其所以受我 圣考旷感之褒。致吾宗国守义之美者。安知其
以管领其花叶。而益寓羹墙之慕。既岁久而圮则鸠财于一路章甫。又为之重新而敞其制。名之曰花叶楼。将以今端阳落之。要宗鲁记其事。自惟藐末何敢当。但夙抱执鞭之愿。幸而得托名文字之间亦荣矣。故遂不辞而为之说曰呜呼。先生得天地至大至刚之气。其直养于平居。而卓立于昏朝者。既已质圣贤确金石而无歉。乃若为 大明扶植万古之纲常。虽古鲁连子,文丞相。莫之过也。此皆载于国乘。播于野史。千百世之下。亦当仰之若泰山北斗。而无容更赘。惟其隐于某里之后。自以腹剑不死。为没身之恨。目不接异历。惟以花开叶落。验夫四时之移者。其炳炳赤衷。盖与红罗岁月相终始。则先生虽自谓崇祯年号止于斯。吾知某里之花叶长存。则 皇朝一统之历。亦与之不亡矣。后之游斯楼者。其无以等閒开落视之。一区某里。以为是 朱氏乾坤。而寓夫子春秋之义可也。若然者先生之大节。尚矣勿论。即此一句诗。其树风声于万世者。亦为如何哉。是则斯楼之以花叶名诚宜矣。而先生陟降之灵。其必眷顾低徊于此。抚玆时物。念彼周京。宜无异于平日。则其所以受我 圣考旷感之褒。致吾宗国守义之美者。安知其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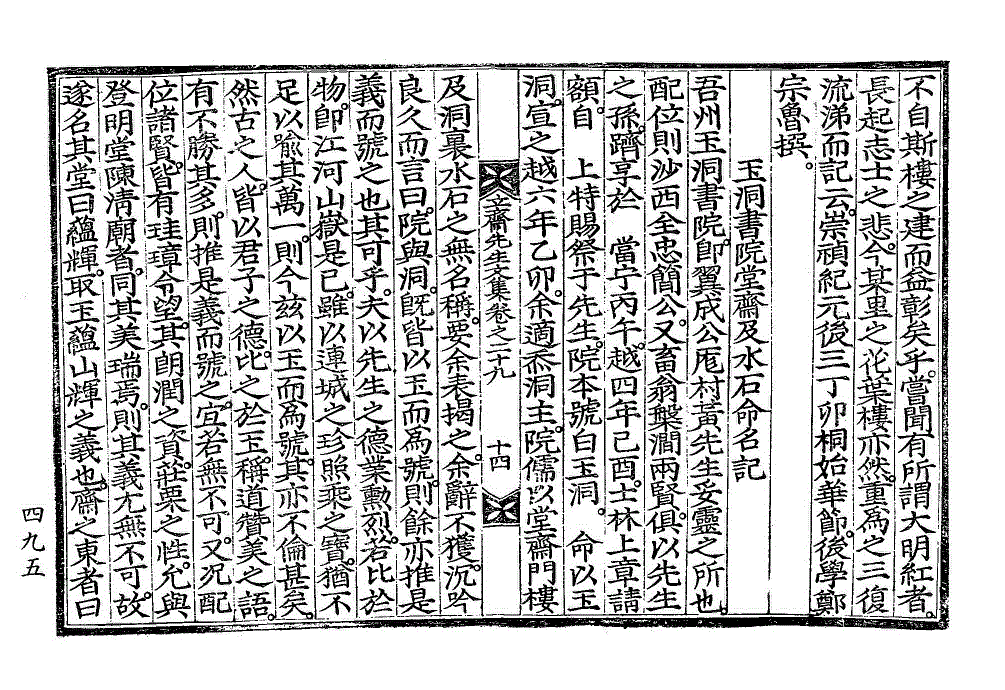 不自斯楼之建而益彰矣乎。尝闻有所谓大明红者。长起志士之悲。今某里之花叶楼亦然。重为之三复流涕而记云。崇祯纪元后三丁卯桐始华节。后学郑宗鲁撰。
不自斯楼之建而益彰矣乎。尝闻有所谓大明红者。长起志士之悲。今某里之花叶楼亦然。重为之三复流涕而记云。崇祯纪元后三丁卯桐始华节。后学郑宗鲁撰。玉洞书院堂斋及水石命名记
吾州玉洞书院。即翼成公厖村黄先生妥灵之所也。配位则沙西全忠简公。又畜翁槃涧两贤。俱以先生之孙。跻享于 当宁丙午。越四年己酉。士林上章请额。自 上特赐祭于先生。院本号白玉洞。 命以玉洞。宣之越六年乙卯。余适忝洞主。院儒以堂斋门楼及洞里水石之无名称。要余表揭之。余辞不获。沉吟良久而言曰。院与洞。既皆以玉而为号。则馀亦推是义而号之也其可乎。夫以先生之德业勋烈。若比于物。即江河山岳是已。虽以连城之珍照乘之宝。犹不足以喻其万一。则今玆以玉而为号。其亦不伦甚矣。然古之人。皆以君子之德。比之于玉。称道赞美之语。有不胜其多。则推是义而号之。宜若无不可。又况配位诸贤。皆有圭璋令望。其朗润之资。庄栗之性。允与登明堂陈清庙者。同其美瑞焉。则其义尤无不可。故遂名其堂曰蕴辉。取玉蕴山辉之义也。斋之东者曰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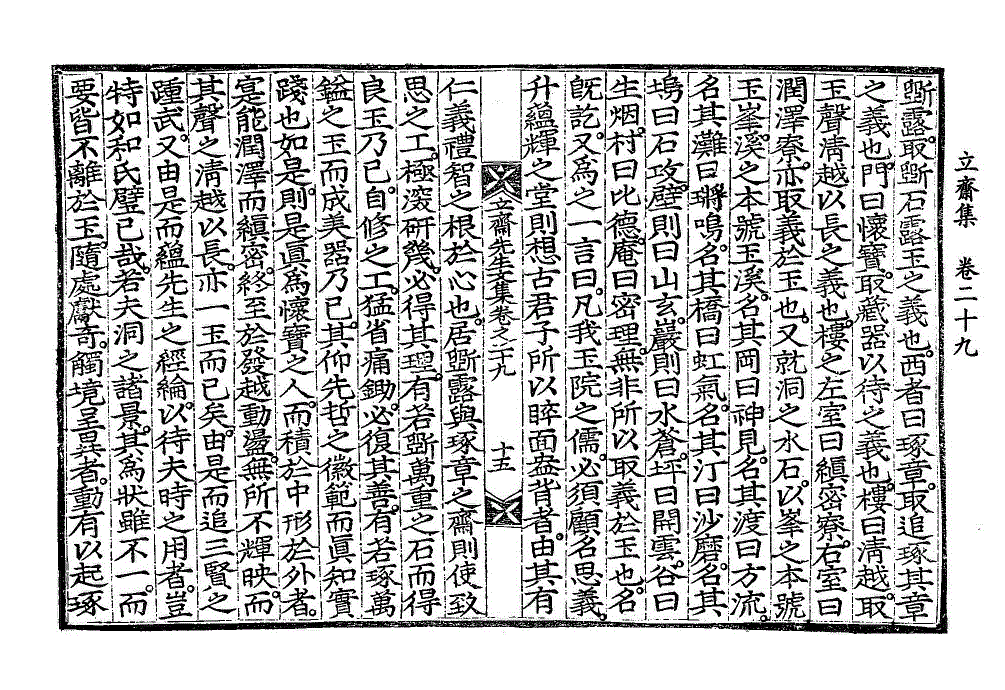 斲露。取斲石露玉之义也。西者曰琢章。取追琢其章之义也。门曰怀宝。取藏器以待之义也。楼曰清越。取玉声清越以长之义也。楼之左室曰缜密寮。右室曰润泽寮。亦取义于玉也。又就洞之水石。以峰之本号玉峰。溪之本号玉溪。名其冈曰神见。名其渡曰方流。名其滩曰𤨿鸣。名其桥曰虹气。名其汀曰沙磨。名其坞曰石攻。壁则曰山玄。岩则曰水苍。坪曰开云。谷曰生烟。村曰比德。庵曰密理。无非所以取义于玉也。名既讫。又为之一言曰。凡我玉院之儒。必须顾名思义。升蕴辉之堂则想古君子所以睟面盎背者。由其有仁义礼智之根于心也。居斲露与琢章之斋则使致思之工。极深研几。必得其理。有若斲万重之石而得良玉乃已。自修之工。猛省痛锄。必复其善。有若琢万镒之玉而成美器乃已。其仰先哲之徽范而真知实践也如是。则是真为怀宝之人。而积于中形于外者。寔能润泽而缜密。终至于发越动荡。无所不辉映。而其声之清越以长。亦一玉而已矣。由是而追三贤之踵武。又由是而蕴先生之经纶。以待夫时之用者。岂特如和氏璧已哉。若夫洞之诸景。其为状虽不一。而要皆不离于玉。随处献奇。触境呈异者。动有以起琢
斲露。取斲石露玉之义也。西者曰琢章。取追琢其章之义也。门曰怀宝。取藏器以待之义也。楼曰清越。取玉声清越以长之义也。楼之左室曰缜密寮。右室曰润泽寮。亦取义于玉也。又就洞之水石。以峰之本号玉峰。溪之本号玉溪。名其冈曰神见。名其渡曰方流。名其滩曰𤨿鸣。名其桥曰虹气。名其汀曰沙磨。名其坞曰石攻。壁则曰山玄。岩则曰水苍。坪曰开云。谷曰生烟。村曰比德。庵曰密理。无非所以取义于玉也。名既讫。又为之一言曰。凡我玉院之儒。必须顾名思义。升蕴辉之堂则想古君子所以睟面盎背者。由其有仁义礼智之根于心也。居斲露与琢章之斋则使致思之工。极深研几。必得其理。有若斲万重之石而得良玉乃已。自修之工。猛省痛锄。必复其善。有若琢万镒之玉而成美器乃已。其仰先哲之徽范而真知实践也如是。则是真为怀宝之人。而积于中形于外者。寔能润泽而缜密。终至于发越动荡。无所不辉映。而其声之清越以长。亦一玉而已矣。由是而追三贤之踵武。又由是而蕴先生之经纶。以待夫时之用者。岂特如和氏璧已哉。若夫洞之诸景。其为状虽不一。而要皆不离于玉。随处献奇。触境呈异者。动有以起琢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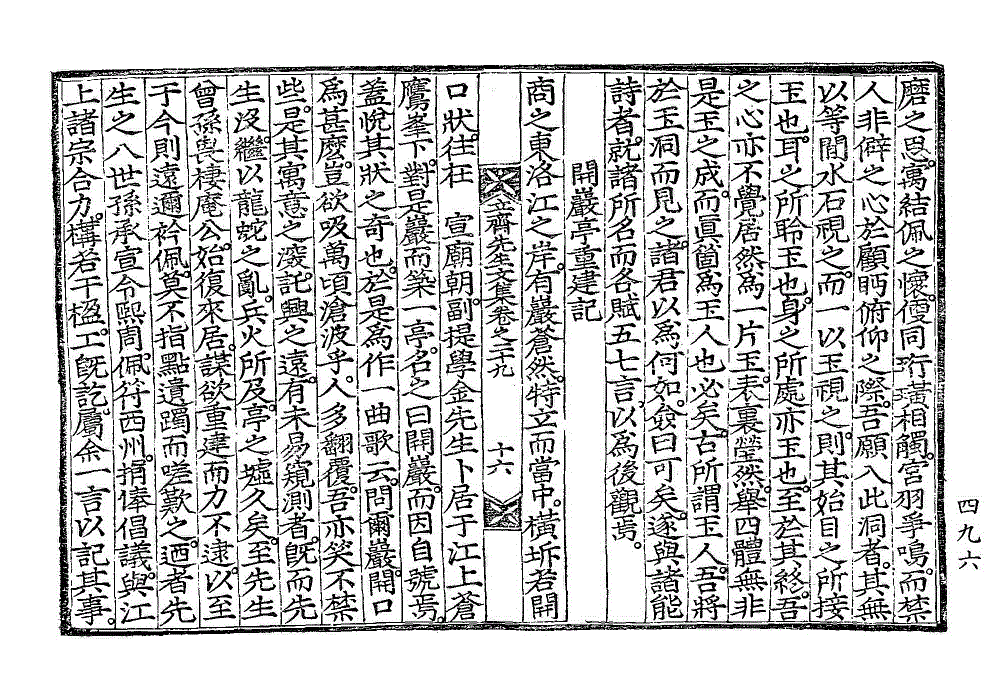 磨之思。寓结佩之怀。便同珩璜相触。宫羽争鸣。而禁人非僻之心于顾眄俯仰之际。吾愿入此洞者。其无以等閒水石视之。而一以玉视之。则其始目之所接玉也。耳之所聆玉也。身之所处亦玉也。至于其终。吾之心亦不觉居然为一片玉。表里莹然。举四体无非是玉之成。而真个为玉人也必矣。古所谓玉人。吾将于玉洞而见之。诸君以为何如。佥曰可矣。遂与诸能诗者。就诸所名而各赋五七言。以为后观焉。
磨之思。寓结佩之怀。便同珩璜相触。宫羽争鸣。而禁人非僻之心于顾眄俯仰之际。吾愿入此洞者。其无以等閒水石视之。而一以玉视之。则其始目之所接玉也。耳之所聆玉也。身之所处亦玉也。至于其终。吾之心亦不觉居然为一片玉。表里莹然。举四体无非是玉之成。而真个为玉人也必矣。古所谓玉人。吾将于玉洞而见之。诸君以为何如。佥曰可矣。遂与诸能诗者。就诸所名而各赋五七言。以为后观焉。开岩亭重建记
商之东洛江之岸。有岩苍然。特立而当中。横坼若开口状。往在 宣庙朝。副提学金先生卜居于江上苍鹰峰下。对是岩而筑一亭。名之曰开岩。而因自号焉。盖悦其状之奇也。于是为作一曲歌云。问尔岩。开口为甚么。岂欲吸万顷沧波乎。人多翻覆。吾亦笑不禁些。是其寓意之深。托兴之远。有未易窥测者。既而先生没。继以龙蛇之乱。兵火所及。亭之墟久矣。至先生曾孙畏栖庵公。始复来居。谋欲重建而力不逮。以至于今则远迩衿佩。莫不指点遗躅而嗟叹之。乃者先生之八世孙承宣令熙周。佩符西州。捐俸倡议。与江上诸宗合力。构若干楹。工既讫。属余一言以记其事。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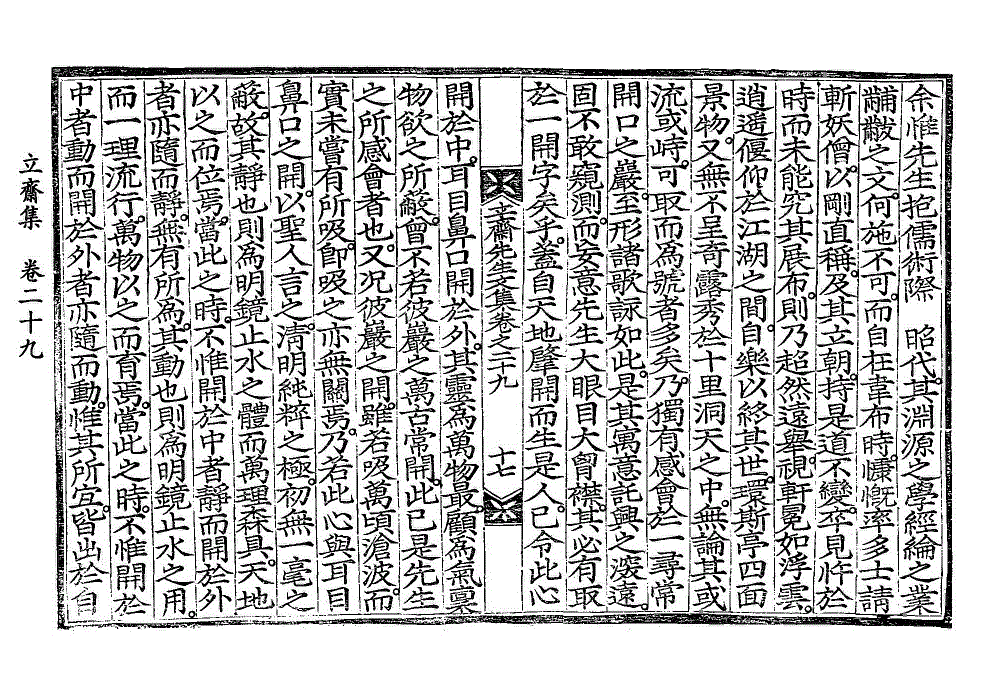 余惟先生抱儒术际 昭代。其渊源之学经纶之业黼黻之文。何施不可。而自在韦布时。慷慨率多士请斩妖僧。以刚直称。及其立朝。持是道不变。卒见忤于时而未能究其展布。则乃超然远举。视轩冕如浮云。逍遥偃仰于江湖之间。自乐以终其世。环斯亭四面景物。又无不呈奇露秀于十里洞天之中。无论其或流或峙。可取而为号者多矣。乃独有感会于一寻常开口之岩。至形诸歌咏如此。是其寓意托兴之深远。固不敢窥测。而妄意先生大眼目大胸襟。其必有取于一开字矣乎。盖自天地肇开而生是人。已令此心开于中。耳目鼻口开于外。其灵为万物最。顾为气禀物欲之所蔽。曾不若彼岩之万古常开。此已是先生之所感会者也。又况彼岩之开。虽若吸万顷沧波。而实未尝有所吸。即吸之亦无关焉。乃若此心与耳目鼻口之开。以圣人言之。清明纯粹之极。初无一毫之蔽。故其静也则为明镜止水之体而万理森具。天地以之而位焉。当此之时。不惟开于中者静而开于外者亦随而静。无有所为。其动也则为明镜止水之用。而一理流行。万物以之而育焉。当此之时。不惟开于中者动而开于外者亦随而动。惟其所宜。皆出于自
余惟先生抱儒术际 昭代。其渊源之学经纶之业黼黻之文。何施不可。而自在韦布时。慷慨率多士请斩妖僧。以刚直称。及其立朝。持是道不变。卒见忤于时而未能究其展布。则乃超然远举。视轩冕如浮云。逍遥偃仰于江湖之间。自乐以终其世。环斯亭四面景物。又无不呈奇露秀于十里洞天之中。无论其或流或峙。可取而为号者多矣。乃独有感会于一寻常开口之岩。至形诸歌咏如此。是其寓意托兴之深远。固不敢窥测。而妄意先生大眼目大胸襟。其必有取于一开字矣乎。盖自天地肇开而生是人。已令此心开于中。耳目鼻口开于外。其灵为万物最。顾为气禀物欲之所蔽。曾不若彼岩之万古常开。此已是先生之所感会者也。又况彼岩之开。虽若吸万顷沧波。而实未尝有所吸。即吸之亦无关焉。乃若此心与耳目鼻口之开。以圣人言之。清明纯粹之极。初无一毫之蔽。故其静也则为明镜止水之体而万理森具。天地以之而位焉。当此之时。不惟开于中者静而开于外者亦随而静。无有所为。其动也则为明镜止水之用。而一理流行。万物以之而育焉。当此之时。不惟开于中者动而开于外者亦随而动。惟其所宜。皆出于自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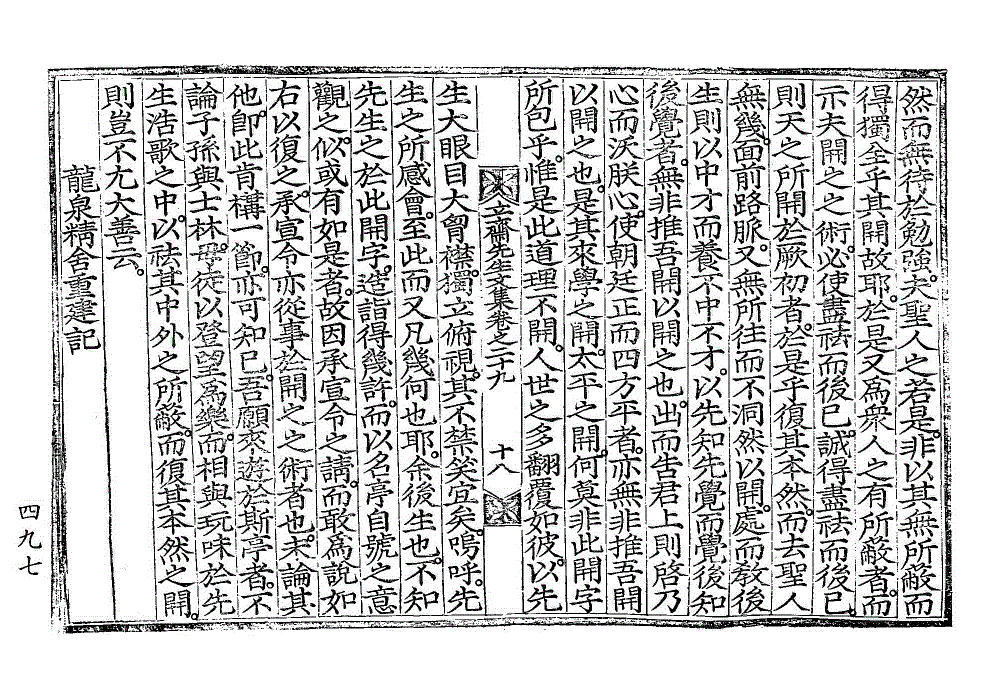 然而无待于勉强。夫圣人之若是。非以其无所蔽而得独全乎其开故耶。于是又为众人之有所蔽者。而示夫开之之术。必使尽祛而后已。诚得尽祛而后已。则天之所开于厥初者。于是乎复其本然。而去圣人无几。面前路脉。又无所往而不洞然以开。处而教后生则以中才而养不中不才。以先知先觉而觉后知后觉者。无非推吾开以开之也。出而告君上则启乃心而沃朕心。使朝廷正而四方平者。亦无非推吾开以开之也。是其来学之开。太平之开。何莫非此开字所包乎。惟是此道理不开。人世之多翻覆如彼。以先生大眼目大胸襟。独立俯视。其不禁笑宜矣。呜呼。先生之所感会。至此而又凡几何也耶。余后生也。不知先生之于此开字。造诣得几许。而以名亭自号之意观之。似或有如是者。故因承宣令之请。而敢为说如右以复之。承宣令亦从事于开之之术者也。未论其他。即此肯构一节。亦可知已。吾愿来游于斯亭者。不论子孙与士林。毋徒以登望为乐。而相与玩味于先生浩歌之中。以祛其中外之所蔽。而复其本然之开。则岂不尤大善云。
然而无待于勉强。夫圣人之若是。非以其无所蔽而得独全乎其开故耶。于是又为众人之有所蔽者。而示夫开之之术。必使尽祛而后已。诚得尽祛而后已。则天之所开于厥初者。于是乎复其本然。而去圣人无几。面前路脉。又无所往而不洞然以开。处而教后生则以中才而养不中不才。以先知先觉而觉后知后觉者。无非推吾开以开之也。出而告君上则启乃心而沃朕心。使朝廷正而四方平者。亦无非推吾开以开之也。是其来学之开。太平之开。何莫非此开字所包乎。惟是此道理不开。人世之多翻覆如彼。以先生大眼目大胸襟。独立俯视。其不禁笑宜矣。呜呼。先生之所感会。至此而又凡几何也耶。余后生也。不知先生之于此开字。造诣得几许。而以名亭自号之意观之。似或有如是者。故因承宣令之请。而敢为说如右以复之。承宣令亦从事于开之之术者也。未论其他。即此肯构一节。亦可知已。吾愿来游于斯亭者。不论子孙与士林。毋徒以登望为乐。而相与玩味于先生浩歌之中。以祛其中外之所蔽。而复其本然之开。则岂不尤大善云。龙泉精舍重建记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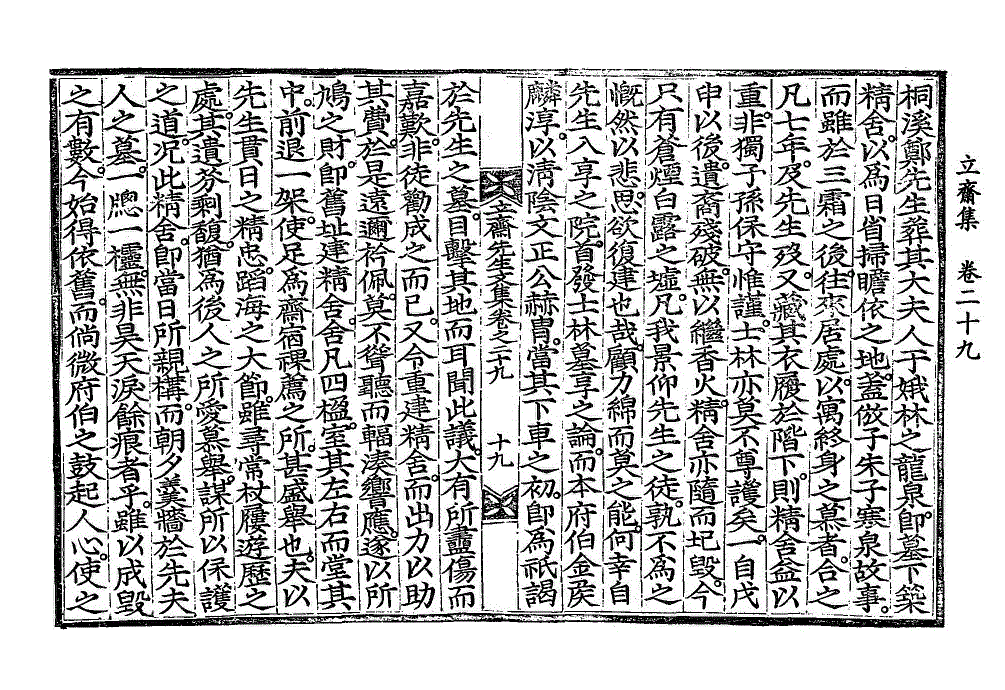 桐溪郑先生葬其大夫人于娥林之龙泉。即墓下筑精舍。以为日省扫瞻依之地。盖仿子朱子寒泉故事。而虽于三霜之后。往来居处。以寓终身之慕者。合之凡七年。及先生殁。又藏其衣履于阶下。则精舍益以重。非独子孙保守惟谨。士林亦莫不尊护矣。一自戊申以后。遗裔残破。无以继香火。精舍亦随而圮毁。今只有苍烟白露之墟。凡我景仰先生之徒。孰不为之慨然以悲。思欲复建也哉。顾力绵而莫之能。何幸自先生入享之院。首发士林墓享之论。而本府伯金侯麟淳。以清阴文正公赫胄。当其下车之初。即为祇谒于先生之墓。目击其地而耳闻此议。大有所衋伤而嘉叹。非徒劝成之而已。又令重建精舍。而出力以助其费。于是远迩衿佩。莫不耸听而辐凑响应。遂以所鸠之财。即旧址建精舍。舍凡四楹。室其左右而堂其中。前退一架。使足为斋宿祼荐之所。甚盛举也。夫以先生贯日之精忠。蹈海之大节。虽寻常杖屦游历之处。其遗芬剩馥。犹为后人之所爱慕举。谋所以保护之道。况此精舍。即当日所亲构。而朝夕羹墙于先夫人之墓。一窗一棂。无非昊天泪馀痕者乎。虽以成毁之有数。今始得依旧。而倘微府伯之鼓起人心。使之
桐溪郑先生葬其大夫人于娥林之龙泉。即墓下筑精舍。以为日省扫瞻依之地。盖仿子朱子寒泉故事。而虽于三霜之后。往来居处。以寓终身之慕者。合之凡七年。及先生殁。又藏其衣履于阶下。则精舍益以重。非独子孙保守惟谨。士林亦莫不尊护矣。一自戊申以后。遗裔残破。无以继香火。精舍亦随而圮毁。今只有苍烟白露之墟。凡我景仰先生之徒。孰不为之慨然以悲。思欲复建也哉。顾力绵而莫之能。何幸自先生入享之院。首发士林墓享之论。而本府伯金侯麟淳。以清阴文正公赫胄。当其下车之初。即为祇谒于先生之墓。目击其地而耳闻此议。大有所衋伤而嘉叹。非徒劝成之而已。又令重建精舍。而出力以助其费。于是远迩衿佩。莫不耸听而辐凑响应。遂以所鸠之财。即旧址建精舍。舍凡四楹。室其左右而堂其中。前退一架。使足为斋宿祼荐之所。甚盛举也。夫以先生贯日之精忠。蹈海之大节。虽寻常杖屦游历之处。其遗芬剩馥。犹为后人之所爱慕举。谋所以保护之道。况此精舍。即当日所亲构。而朝夕羹墙于先夫人之墓。一窗一棂。无非昊天泪馀痕者乎。虽以成毁之有数。今始得依旧。而倘微府伯之鼓起人心。使之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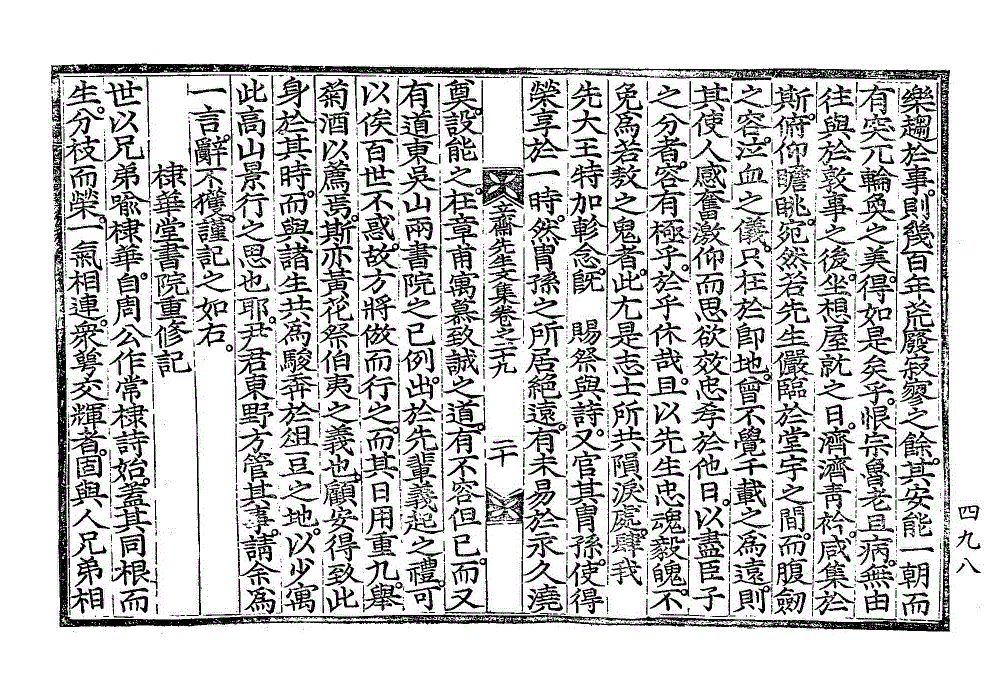 乐趋于事。则几百年荒废寂寥之馀。其安能一朝而有突兀轮奂之美。得如是矣乎。恨宗鲁老且病。无由往与于敦事之后。坐想屋就之日。济济青衿。咸集于斯。俯仰瞻眺。宛然若先生俨临于堂宇之间。而腹剑之容。泣血之仪。只在于即地。曾不觉千载之为远。则其使人感奋激仰而思欲效忠孝于他日。以尽臣子之分者。容有极乎。于乎休哉。且以先生忠魂毅魄。不免为若敖之鬼者。此尤是志士所共陨泪处。肆我 先大王特加轸念。既 赐祭与诗。又官其胄孙。使得荣享于一时。然胄孙之所居绝远。有未易于永久浇奠。设能之。在章甫寓慕致诚之道。有不容但已。而又有道东吴山两书院之已例。出于先辈义起之礼。可以俟百世不惑。故方将仿而行之。而其日用重九。举菊酒以荐焉。斯亦黄花祭伯夷之义也。顾安得致此身于其时。而与诸生共为骏奔于俎豆之地。以少寓此高山景行之思也耶。尹君东野方管其事。请余为一言。辞不获。谨记之如右。
乐趋于事。则几百年荒废寂寥之馀。其安能一朝而有突兀轮奂之美。得如是矣乎。恨宗鲁老且病。无由往与于敦事之后。坐想屋就之日。济济青衿。咸集于斯。俯仰瞻眺。宛然若先生俨临于堂宇之间。而腹剑之容。泣血之仪。只在于即地。曾不觉千载之为远。则其使人感奋激仰而思欲效忠孝于他日。以尽臣子之分者。容有极乎。于乎休哉。且以先生忠魂毅魄。不免为若敖之鬼者。此尤是志士所共陨泪处。肆我 先大王特加轸念。既 赐祭与诗。又官其胄孙。使得荣享于一时。然胄孙之所居绝远。有未易于永久浇奠。设能之。在章甫寓慕致诚之道。有不容但已。而又有道东吴山两书院之已例。出于先辈义起之礼。可以俟百世不惑。故方将仿而行之。而其日用重九。举菊酒以荐焉。斯亦黄花祭伯夷之义也。顾安得致此身于其时。而与诸生共为骏奔于俎豆之地。以少寓此高山景行之思也耶。尹君东野方管其事。请余为一言。辞不获。谨记之如右。棣华堂书院重修记
世以兄弟喻棣华。自周公作常棣诗始。盖其同根而生。分枝而荣。一气相连。众萼交辉者。固与人兄弟相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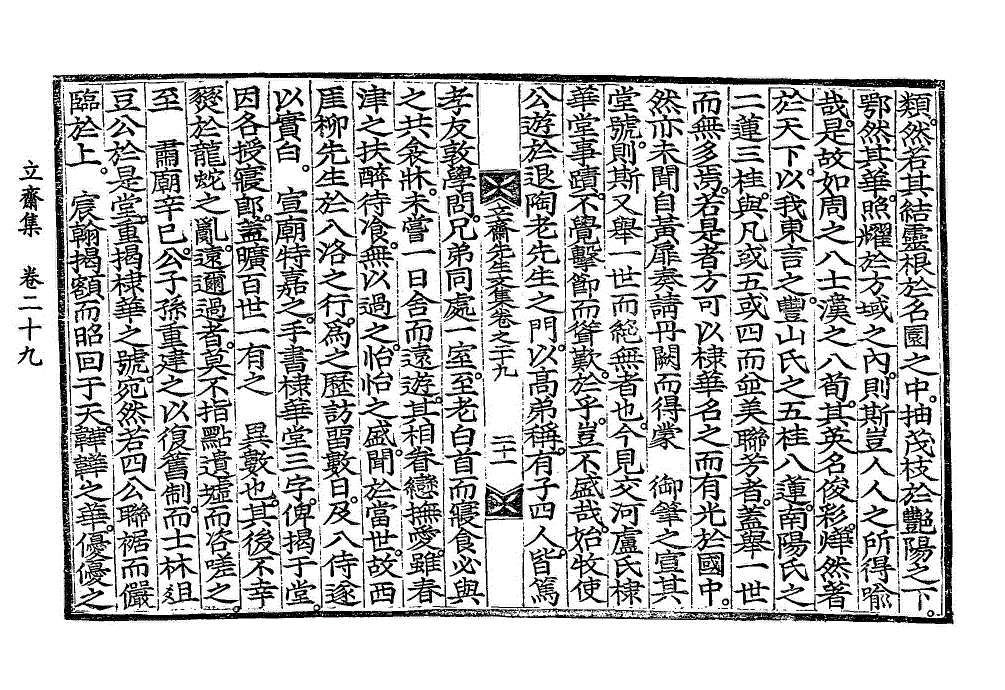 类。然若其结灵根于名园之中。抽茂枝于艳阳之下。鄂然其华。照耀于方域之内。则斯岂人人之所得喻哉。是故如周之八士汉之八荀。其英名俊彩。烨然著于天下。以我东言之。丰山氏之五桂八莲。南阳氏之二莲三桂。与凡或五或四而并美联芳者。盖举一世而无多焉。若是者方可以棣华名之而有光于国中。然亦未闻自黄扉奏请丹阙而得蒙 御笔之宣其堂号。则斯又举一世而绝无者也。今见交河卢氏棣华堂事迹。不觉击节而耸叹。于乎。岂不盛哉。始牧使公游于退陶老先生之门。以高弟称。有子四人。皆笃孝友敦学问。兄弟同处一室。至老白首而寝食必与之共衾床。未尝一日舍而远游。其相眷恋抚爱。虽春津之扶醉待餐。无以过之。怡怡之盛。闻于当世。故西厓柳先生于入洛之行。为之历访留数日。及入侍遂以实白。 宣庙特嘉之。手书棣华堂三字。俾揭于堂。因各授寝郎。盖旷百世一有之 异数也。其后不幸燹于龙蛇之乱。远迩过者。莫不指点遗墟而咨嗟之。至 肃庙辛巳。公子孙重建之以复旧制。而士林俎豆公于是堂。重揭棣华之号。宛然若四公联裾而俨临于上。 宸翰揭额而昭回于天。韡韡之华。优优之
类。然若其结灵根于名园之中。抽茂枝于艳阳之下。鄂然其华。照耀于方域之内。则斯岂人人之所得喻哉。是故如周之八士汉之八荀。其英名俊彩。烨然著于天下。以我东言之。丰山氏之五桂八莲。南阳氏之二莲三桂。与凡或五或四而并美联芳者。盖举一世而无多焉。若是者方可以棣华名之而有光于国中。然亦未闻自黄扉奏请丹阙而得蒙 御笔之宣其堂号。则斯又举一世而绝无者也。今见交河卢氏棣华堂事迹。不觉击节而耸叹。于乎。岂不盛哉。始牧使公游于退陶老先生之门。以高弟称。有子四人。皆笃孝友敦学问。兄弟同处一室。至老白首而寝食必与之共衾床。未尝一日舍而远游。其相眷恋抚爱。虽春津之扶醉待餐。无以过之。怡怡之盛。闻于当世。故西厓柳先生于入洛之行。为之历访留数日。及入侍遂以实白。 宣庙特嘉之。手书棣华堂三字。俾揭于堂。因各授寝郎。盖旷百世一有之 异数也。其后不幸燹于龙蛇之乱。远迩过者。莫不指点遗墟而咨嗟之。至 肃庙辛巳。公子孙重建之以复旧制。而士林俎豆公于是堂。重揭棣华之号。宛然若四公联裾而俨临于上。 宸翰揭额而昭回于天。韡韡之华。优优之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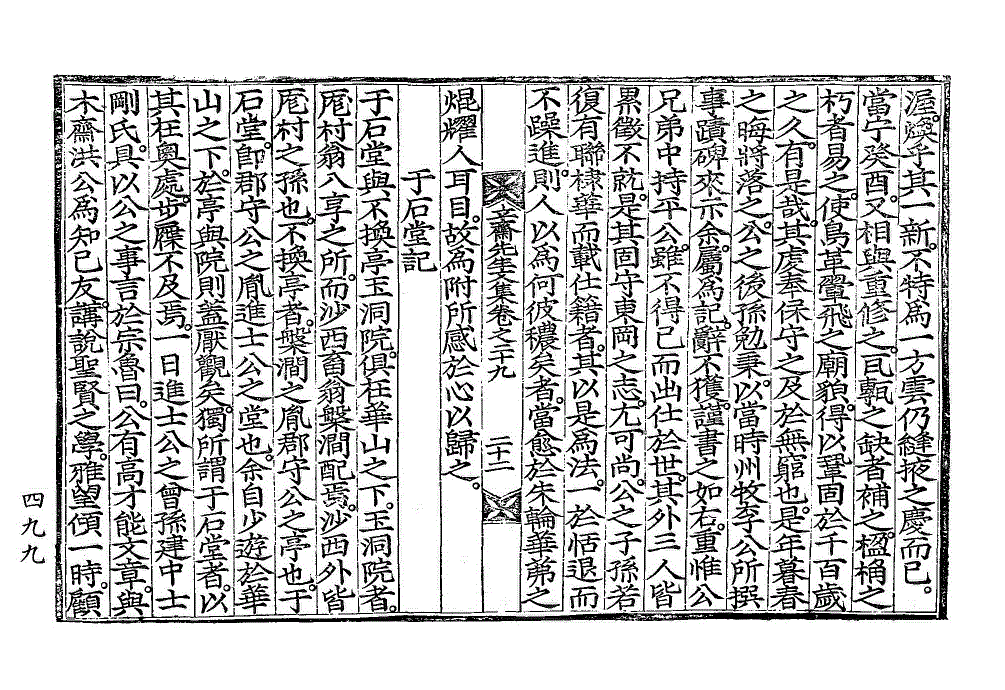 渥。焕乎其一新。不特为一方云仍缝掖之庆而已。 当宁癸酉。又相与重修之。瓦砖之缺者补之。楹桷之朽者易之。使鸟革翚飞之庙貌。得以巩固于千百岁之久。有是哉。其虔奉保守之及于无穷也。是年暮春之晦将落之。公之后孙勉秉。以当时州牧李公所撰事迹碑来示余。属为记。辞不获。谨书之如右。重惟公兄弟中持平公。虽不得已而出仕于世。其外三人皆累徵不就。是其固守东冈之志。尤可尚。公之子孙若复有联棣华而载仕籍者。其以是为法。一于恬退而不躁进。则人以为何彼秾矣者。当愈于朱轮华茀之焜耀人耳目。故为附所感于心以归之。
渥。焕乎其一新。不特为一方云仍缝掖之庆而已。 当宁癸酉。又相与重修之。瓦砖之缺者补之。楹桷之朽者易之。使鸟革翚飞之庙貌。得以巩固于千百岁之久。有是哉。其虔奉保守之及于无穷也。是年暮春之晦将落之。公之后孙勉秉。以当时州牧李公所撰事迹碑来示余。属为记。辞不获。谨书之如右。重惟公兄弟中持平公。虽不得已而出仕于世。其外三人皆累徵不就。是其固守东冈之志。尤可尚。公之子孙若复有联棣华而载仕籍者。其以是为法。一于恬退而不躁进。则人以为何彼秾矣者。当愈于朱轮华茀之焜耀人耳目。故为附所感于心以归之。于石堂记
于石堂与不换亭玉洞院。俱在华山之下。玉洞院者。厖村翁入享之所。而沙西畜翁槃涧配焉。沙西外皆厖村之孙也。不换亭者。槃涧之胤郡守公之亭也。于石堂。即郡守公之胤进士公之堂也。余自少游于华山之下。于亭与院则盖厌观矣。独所谓于石堂者。以其在奥处。步屧不及焉。一日进士公之曾孙建中士刚氏。具以公之事言于宗鲁曰。公有高才能文章。与木斋洪公为知己友。讲说圣贤之学。雅望倾一时。顾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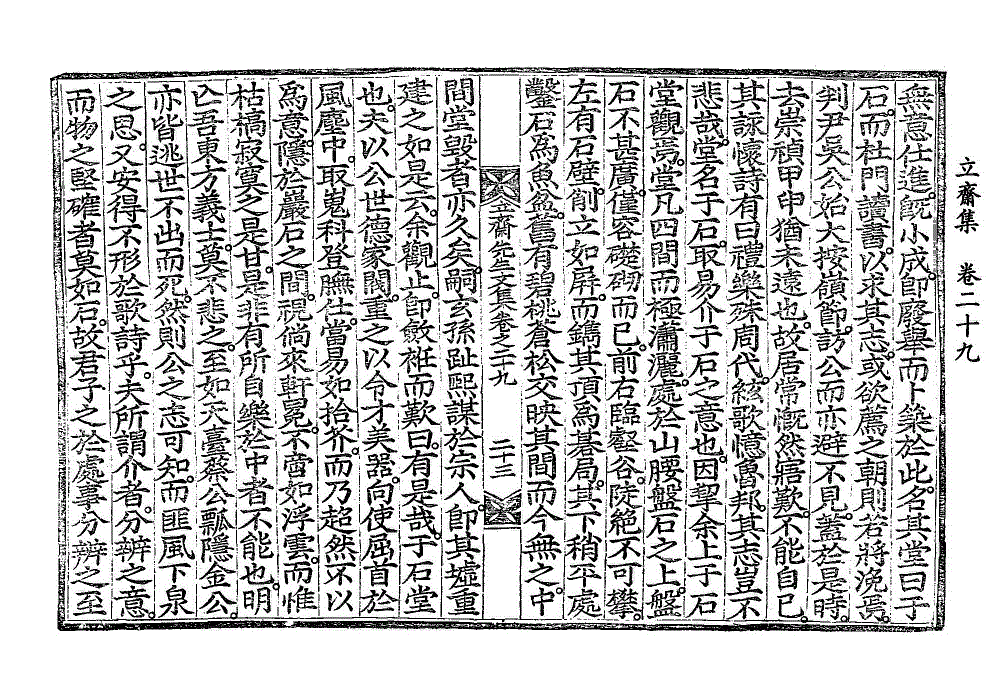 无意仕进。既小成。即废举而卜筑于此。名其堂曰于石。而杜门读书。以求其志。或欲荐之朝则若将浼焉。判尹吴公始大按岭节。访公而亦避不见。盖于是时。去崇祯甲申犹未远也。故居常慨然寤叹。不能自已。其咏怀诗有曰礼乐殊周代。弦歌忆鲁邦。其志岂不悲哉。堂名于石。取易介于石之意也。因挈余上于石堂观焉。堂凡四间而极潇洒。处于山腰盘石之上。盘石不甚广。仅容础砌而已。前右临壑谷。陡绝不可攀。左有石壁。削立如屏。而镌其顶为棋局。其下稍平处凿石为鱼盆。旧有碧桃苍松交映其间而今无之。中间堂毁者亦久矣。嗣玄孙趾熙谋于宗人。即其墟重建之如是云。余观止。即敛衽而叹曰。有是哉。于石堂也。夫以公世德家阀。重之以令才美器。向使屈首于风尘中。取嵬科登膴仕。当易如拾芥。而乃超然不以为意。隐于岩石之间。视倘来轩冕。不啻如浮云。而惟枯槁寂寞之是甘。是非有所自乐于中者不能也。明亡吾东方义士。莫不悲之。至如天台蔡公瓢隐金公。亦皆逃世不出而死。然则公之志可知。而匪风下泉之思。又安得不形于歌诗乎。夫所谓介者。分辨之意。而物之坚确者莫如石。故君子之于处事分辨之至
无意仕进。既小成。即废举而卜筑于此。名其堂曰于石。而杜门读书。以求其志。或欲荐之朝则若将浼焉。判尹吴公始大按岭节。访公而亦避不见。盖于是时。去崇祯甲申犹未远也。故居常慨然寤叹。不能自已。其咏怀诗有曰礼乐殊周代。弦歌忆鲁邦。其志岂不悲哉。堂名于石。取易介于石之意也。因挈余上于石堂观焉。堂凡四间而极潇洒。处于山腰盘石之上。盘石不甚广。仅容础砌而已。前右临壑谷。陡绝不可攀。左有石壁。削立如屏。而镌其顶为棋局。其下稍平处凿石为鱼盆。旧有碧桃苍松交映其间而今无之。中间堂毁者亦久矣。嗣玄孙趾熙谋于宗人。即其墟重建之如是云。余观止。即敛衽而叹曰。有是哉。于石堂也。夫以公世德家阀。重之以令才美器。向使屈首于风尘中。取嵬科登膴仕。当易如拾芥。而乃超然不以为意。隐于岩石之间。视倘来轩冕。不啻如浮云。而惟枯槁寂寞之是甘。是非有所自乐于中者不能也。明亡吾东方义士。莫不悲之。至如天台蔡公瓢隐金公。亦皆逃世不出而死。然则公之志可知。而匪风下泉之思。又安得不形于歌诗乎。夫所谓介者。分辨之意。而物之坚确者莫如石。故君子之于处事分辨之至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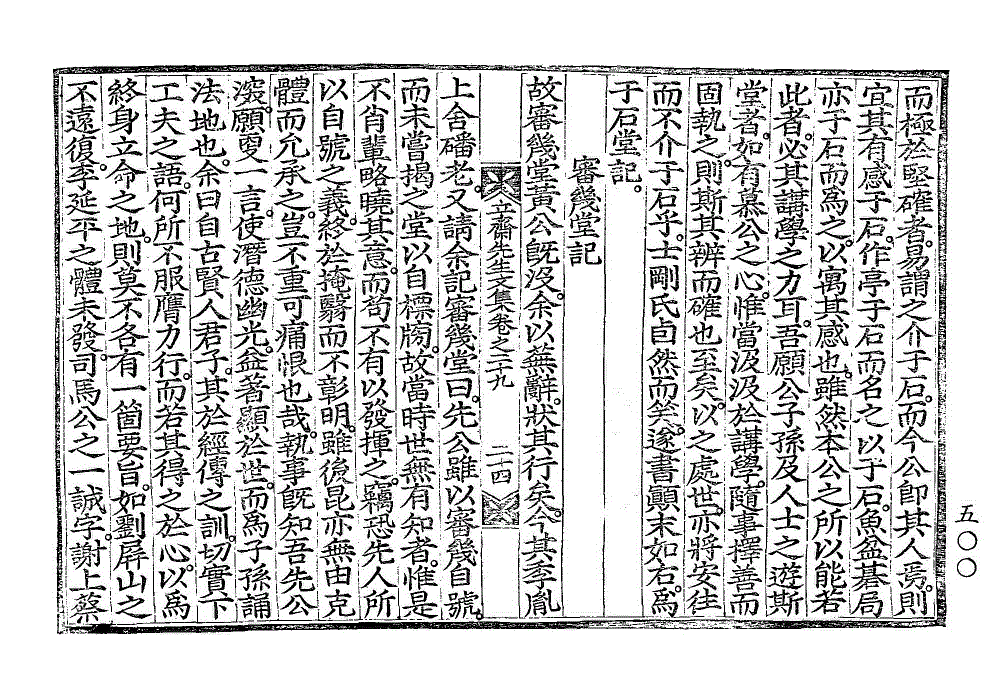 而极于坚确者。易谓之介于石。而今公即其人焉。则宜其有感于石。作亭于石而名之以于石。鱼盆棋局亦于石而为之。以寓其感也。虽然本公之所以能若此者。必其讲学之力耳。吾愿公子孙及人士之游斯堂者。如有慕公之心。惟当汲汲于讲学。随事择善而固执之。则斯其辨而确也至矣。以之处世。亦将安往而不介于石乎。士刚氏卣然而笑。遂书颠末如右。为于石堂记。
而极于坚确者。易谓之介于石。而今公即其人焉。则宜其有感于石。作亭于石而名之以于石。鱼盆棋局亦于石而为之。以寓其感也。虽然本公之所以能若此者。必其讲学之力耳。吾愿公子孙及人士之游斯堂者。如有慕公之心。惟当汲汲于讲学。随事择善而固执之。则斯其辨而确也至矣。以之处世。亦将安往而不介于石乎。士刚氏卣然而笑。遂书颠末如右。为于石堂记。审几堂记
故审几堂黄公既没。余以芜辞。状其行矣。今其季胤上舍磻老。又请余记审几堂曰。先公虽以审几自号。而未尝揭之堂以自标榜。故当时世无有知者。惟是不肖辈略晓其意。而苟不有以发挥之。窃恐先人所以自号之义。终于掩翳而不彰明。虽后昆亦无由克体而允承之。岂不重可痛恨也哉。执事既知吾先公深。愿更一言。使潜德幽光。益著显于世。而为子孙诵法地也。余曰自古贤人君子。其于经传之训。切实下工夫之语。何所不服膺力行。而若其得之于心。以为终身立命之地。则莫不各有一个要旨。如刘屏山之不远复。李延平之体未发。司马公之一诚字。谢上蔡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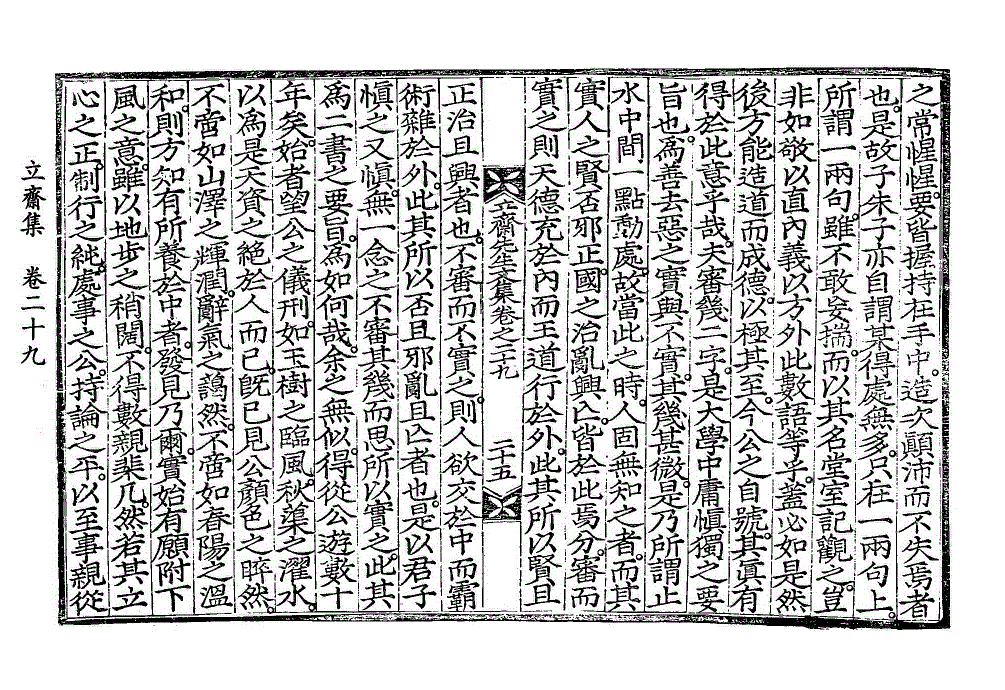 之常惺惺。要皆握持在手中。造次颠沛而不失焉者也。是故子朱子亦自谓某得处无多。只在一两句上。所谓一两句。虽不敢妄揣。而以其名堂室记观之。岂非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数语等乎。盖必如是然后方能造道而成德。以极其至。今公之自号。其真有得于此意乎哉。夫审几二字。是大学中庸慎独之要旨也。为善去恶之实与不实。其几甚微。是乃所谓止水中间一点动处。故当此之时。人固无知之者。而其实人之贤否邪正。国之治乱兴亡。皆于此焉分。审而实之则天德充于内而王道行于外。此其所以贤且正治且兴者也。不审而不实之。则人欲交于中而霸术杂于外。此其所以否且邪乱且亡者也。是以君子慎之又慎。无一念之不审其几而思所以实之。此其为二书之要旨。为如何哉。余之无似。得从公游数十年矣。始者望公之仪刑。如玉树之临风。秋蕖之濯水。以为是天资之绝于人而已。既已见公颜色之睟然。不啻如山泽之辉润。辞气之蔼然。不啻如春阳之温和。则方知有所养于中者。发见乃尔。实始有愿附下风之意。虽以地步之稍阔。不得数亲棐几。然若其立心之正。制行之纯。处事之公。持论之平。以至事亲从
之常惺惺。要皆握持在手中。造次颠沛而不失焉者也。是故子朱子亦自谓某得处无多。只在一两句上。所谓一两句。虽不敢妄揣。而以其名堂室记观之。岂非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数语等乎。盖必如是然后方能造道而成德。以极其至。今公之自号。其真有得于此意乎哉。夫审几二字。是大学中庸慎独之要旨也。为善去恶之实与不实。其几甚微。是乃所谓止水中间一点动处。故当此之时。人固无知之者。而其实人之贤否邪正。国之治乱兴亡。皆于此焉分。审而实之则天德充于内而王道行于外。此其所以贤且正治且兴者也。不审而不实之。则人欲交于中而霸术杂于外。此其所以否且邪乱且亡者也。是以君子慎之又慎。无一念之不审其几而思所以实之。此其为二书之要旨。为如何哉。余之无似。得从公游数十年矣。始者望公之仪刑。如玉树之临风。秋蕖之濯水。以为是天资之绝于人而已。既已见公颜色之睟然。不啻如山泽之辉润。辞气之蔼然。不啻如春阳之温和。则方知有所养于中者。发见乃尔。实始有愿附下风之意。虽以地步之稍阔。不得数亲棐几。然若其立心之正。制行之纯。处事之公。持论之平。以至事亲从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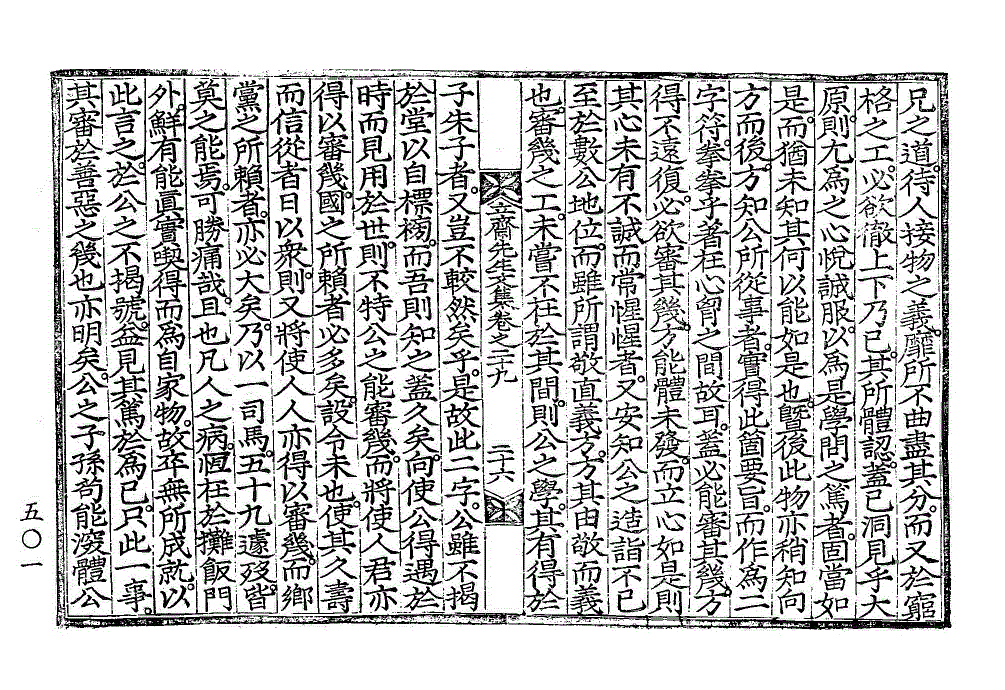 兄之道。待人接物之义。靡所不曲尽其分。而又于穷格之工。必欲彻上下乃已。其所体认。盖已洞见乎大原。则尤为之心悦诚服。以为是学问之笃者。固当如是。而犹未知其何以能如是也。暨后此物亦稍知向方而后。方知公所从事者。实得此个要旨。而作为二字符。拳拳乎著在心胸之间故耳。盖必能审其几。方得不远复。必欲审其几。方能体未发。而立心如是则其心未有不诚而常惺惺者。又安知公之造诣不已至于数公地位。而虽所谓敬直义方。方其由敬而义也。审几之工。未尝不在于其间。则公之学。其有得于子朱子者。又岂不较然矣乎。是故此二字。公虽不揭于堂以自标榜。而吾则知之盖久矣。向使公得遇于时而见用于世。则不特公之能审几。而将使人君亦得以审几。国之所赖者必多矣。设令未也。使其久寿而信从者日以众。则又将使人人亦得以审几。而乡党之所赖者。亦必大矣。乃以一司马。五十九遽殁。皆莫之能焉。可胜痛哉。且也凡人之病。恒在于摊饭门外。鲜有能真实吃得而为自家物。故卒无所成就。以此言之。于公之不揭号。益见其笃于为己。只此一事。其审于善恶之几也亦明矣。公之子孙苟能深体公
兄之道。待人接物之义。靡所不曲尽其分。而又于穷格之工。必欲彻上下乃已。其所体认。盖已洞见乎大原。则尤为之心悦诚服。以为是学问之笃者。固当如是。而犹未知其何以能如是也。暨后此物亦稍知向方而后。方知公所从事者。实得此个要旨。而作为二字符。拳拳乎著在心胸之间故耳。盖必能审其几。方得不远复。必欲审其几。方能体未发。而立心如是则其心未有不诚而常惺惺者。又安知公之造诣不已至于数公地位。而虽所谓敬直义方。方其由敬而义也。审几之工。未尝不在于其间。则公之学。其有得于子朱子者。又岂不较然矣乎。是故此二字。公虽不揭于堂以自标榜。而吾则知之盖久矣。向使公得遇于时而见用于世。则不特公之能审几。而将使人君亦得以审几。国之所赖者必多矣。设令未也。使其久寿而信从者日以众。则又将使人人亦得以审几。而乡党之所赖者。亦必大矣。乃以一司马。五十九遽殁。皆莫之能焉。可胜痛哉。且也凡人之病。恒在于摊饭门外。鲜有能真实吃得而为自家物。故卒无所成就。以此言之。于公之不揭号。益见其笃于为己。只此一事。其审于善恶之几也亦明矣。公之子孙苟能深体公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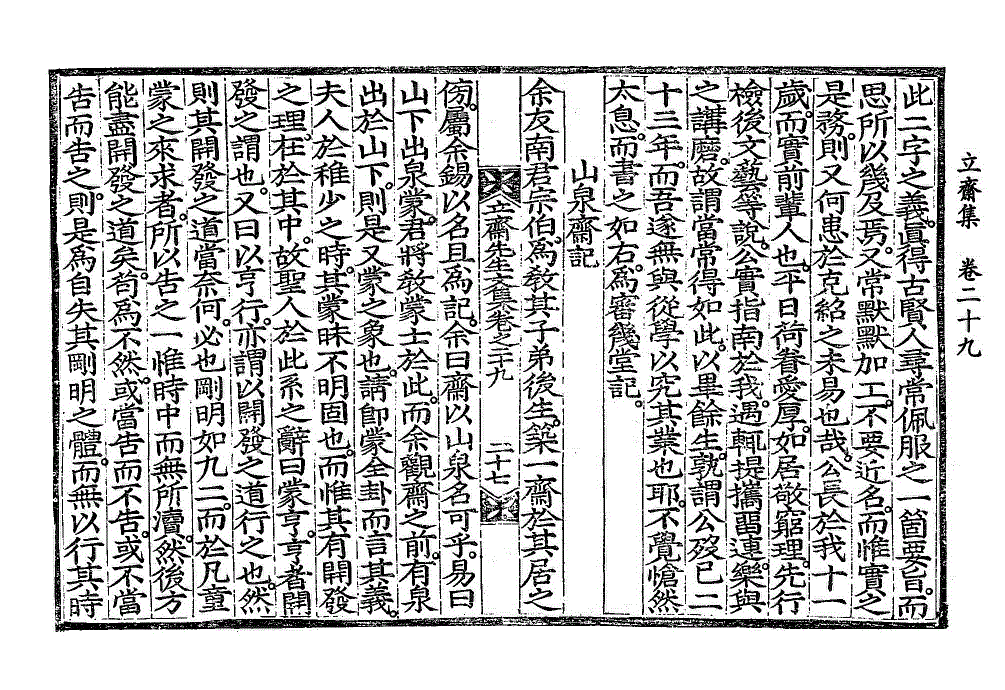 此二字之义。真得古贤人寻常佩服之一个要旨。而思所以几及焉。又常默默加工。不要近名。而惟实之是务。则又何患于克绍之未易也哉。公长于我十一岁。而实前辈人也。平日荷眷爱厚。如居敬穷理。先行检后文艺等说。公实指南于我。遇辄提携留连。乐与之讲磨。故谓当常得如此。以毕馀生。孰谓公殁已二十三年。而吾遂无与从学以究其业也耶。不觉怆然太息。而书之如右。为审几堂记。
此二字之义。真得古贤人寻常佩服之一个要旨。而思所以几及焉。又常默默加工。不要近名。而惟实之是务。则又何患于克绍之未易也哉。公长于我十一岁。而实前辈人也。平日荷眷爱厚。如居敬穷理。先行检后文艺等说。公实指南于我。遇辄提携留连。乐与之讲磨。故谓当常得如此。以毕馀生。孰谓公殁已二十三年。而吾遂无与从学以究其业也耶。不觉怆然太息。而书之如右。为审几堂记。山泉斋记
余友南君宗伯。为教其子弟后生。筑一斋于其居之傍。属余锡以名且为记。余曰斋以山泉名可乎。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将教蒙士于此。而余观斋之前。有泉出于山下。则是又蒙之象也。请即蒙全卦而言其义。夫人于稚少之时。其蒙昧不明固也。而惟其有开发之理。在于其中。故圣人于此系之辞曰蒙亨。亨者开发之谓也。又曰以亨行。亦谓以开发之道行之也。然则其开发之道当奈何。必也刚明如九二。而于凡童蒙之来求者。所以告之一惟时中而无所渎。然后方能尽开发之道矣。苟为不然。或当告而不告。或不当告而告之。则是为自失其刚明之体。而无以行其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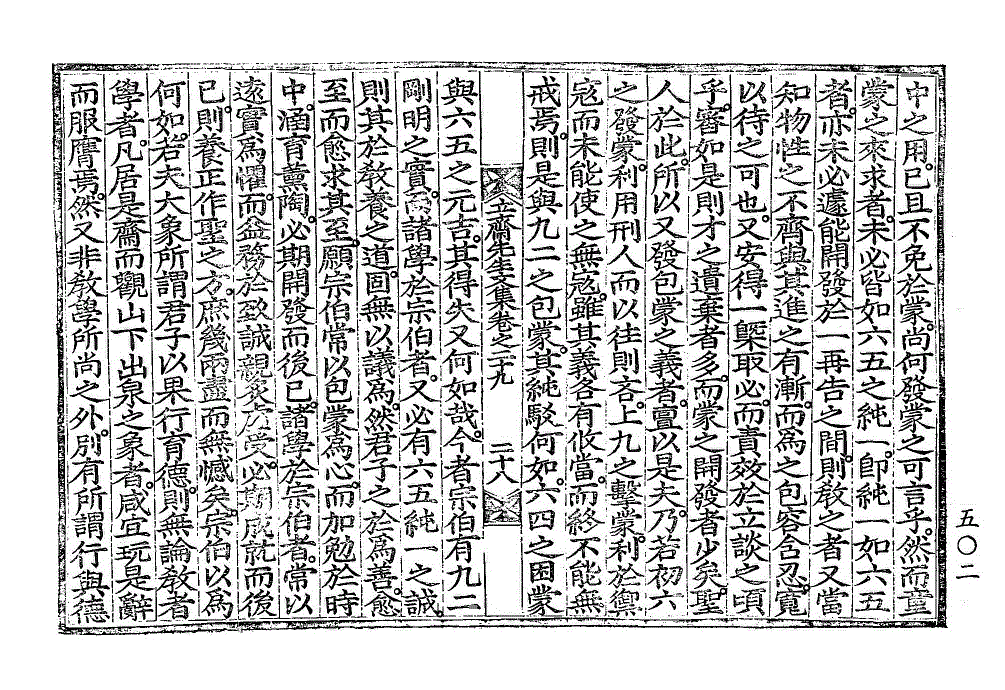 中之用。己且不免于蒙。尚何发蒙之可言乎。然而童蒙之来求者。未必皆如六五之纯一。即纯一如六五者。亦未必遽能开发于一再告之间。则教之者又当知物性之不齐与其进之有渐。而为之包容含忍。宽以待之可也。又安得一槩取必。而责效于立谈之顷乎。审如是则才之遗弃者多。而蒙之开发者少矣。圣人于此。所以又发包蒙之义者。亶以是夫。乃若初六之发蒙。利用刑人而以往则吝。上九之击蒙。利于御寇而未能使之无寇。虽其义各有攸当。而终不能无戒焉。则是与九二之包蒙。其纯驳何如。六四之困蒙与六五之元吉。其得失又何如哉。今者宗伯有九二刚明之实。而诸学于宗伯者。又必有六五纯一之诚。则其于教养之道。固无以议为。然君子之于为善。愈至而愈求其至。愿宗伯常以包蒙为心。而加勉于时中。涵育薰陶。必期开发而后已。诸学于宗伯者。常以远实为惧。而益务于致诚亲炙虚受。必期成就而后已。则养正作圣之方。庶几两尽而无憾矣。宗伯以为何如。若夫大象所谓君子以果行育德。则无论教者学者。凡居是斋而观山下出泉之象者。咸宜玩是辞而服膺焉。然又非教学所尚之外。别有所谓行与德
中之用。己且不免于蒙。尚何发蒙之可言乎。然而童蒙之来求者。未必皆如六五之纯一。即纯一如六五者。亦未必遽能开发于一再告之间。则教之者又当知物性之不齐与其进之有渐。而为之包容含忍。宽以待之可也。又安得一槩取必。而责效于立谈之顷乎。审如是则才之遗弃者多。而蒙之开发者少矣。圣人于此。所以又发包蒙之义者。亶以是夫。乃若初六之发蒙。利用刑人而以往则吝。上九之击蒙。利于御寇而未能使之无寇。虽其义各有攸当。而终不能无戒焉。则是与九二之包蒙。其纯驳何如。六四之困蒙与六五之元吉。其得失又何如哉。今者宗伯有九二刚明之实。而诸学于宗伯者。又必有六五纯一之诚。则其于教养之道。固无以议为。然君子之于为善。愈至而愈求其至。愿宗伯常以包蒙为心。而加勉于时中。涵育薰陶。必期开发而后已。诸学于宗伯者。常以远实为惧。而益务于致诚亲炙虚受。必期成就而后已。则养正作圣之方。庶几两尽而无憾矣。宗伯以为何如。若夫大象所谓君子以果行育德。则无论教者学者。凡居是斋而观山下出泉之象者。咸宜玩是辞而服膺焉。然又非教学所尚之外。别有所谓行与德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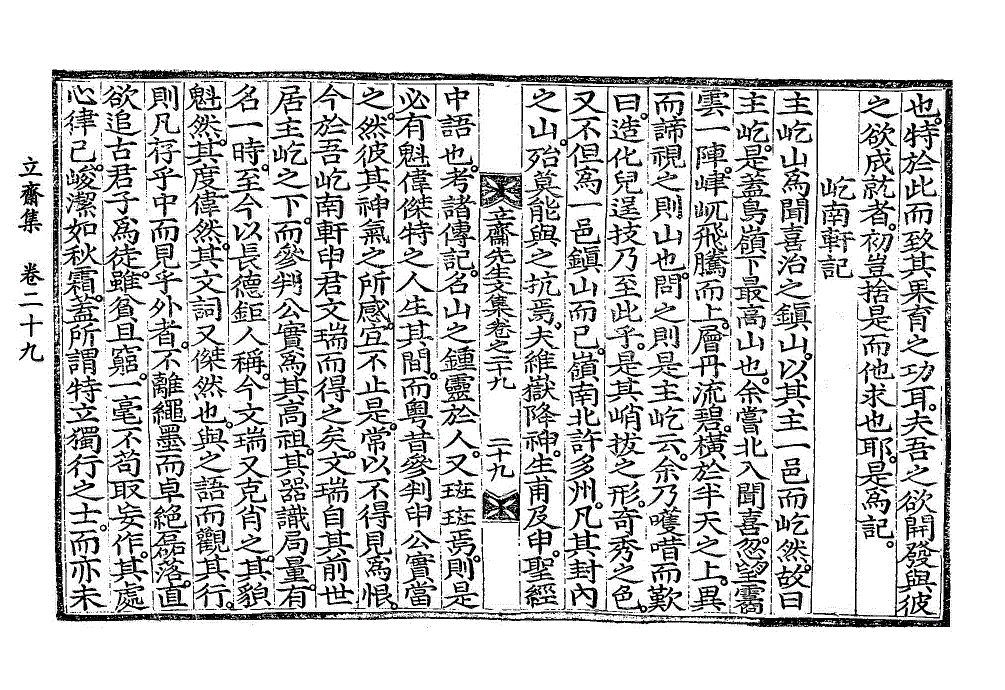 也。特于此而致其果育之功耳。夫吾之欲开发与彼之欲成就者。初岂舍是而他求也耶。是为记。
也。特于此而致其果育之功耳。夫吾之欲开发与彼之欲成就者。初岂舍是而他求也耶。是为记。屹南轩记
主屹山为闻喜治之镇山。以其主一邑而屹然。故曰主屹。是盖鸟岭下最高山也。余尝北入闻喜。忽望霱云一阵。峍屼飞腾而上。层丹流碧。横于半天之上。异而谛视之则山也。问之则是主屹云。余乃嚄唶而叹曰。造化儿逞技乃至此乎。是其峭拔之形。奇秀之色。又不但为一邑镇山而已。岭南北许多州。凡其封内之山。殆莫能与之抗焉。夫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圣经中语也。考诸传记。名山之钟灵于人。又斑斑焉。则是必有魁伟杰特之人生其间。而粤昔参判申公实当之。然彼其神气之所感。宜不止是。常以不得见为恨。今于吾屹南轩申君文瑞而得之矣。文瑞自其前世居主屹之下。而参判公实为其高祖。其器识局量。有名一时。至今以长德钜人称。今文瑞又克肖之。其貌魁然。其度伟然。其文词又杰然也。与之语而观其行。则凡存乎中而见乎外者。不离绳墨而卓绝磊落。直欲追古君子为徒。虽贫且穷。一毫不苟取妄作。其处心律己。峻洁如秋霜。盖所谓特立独行之士。而亦未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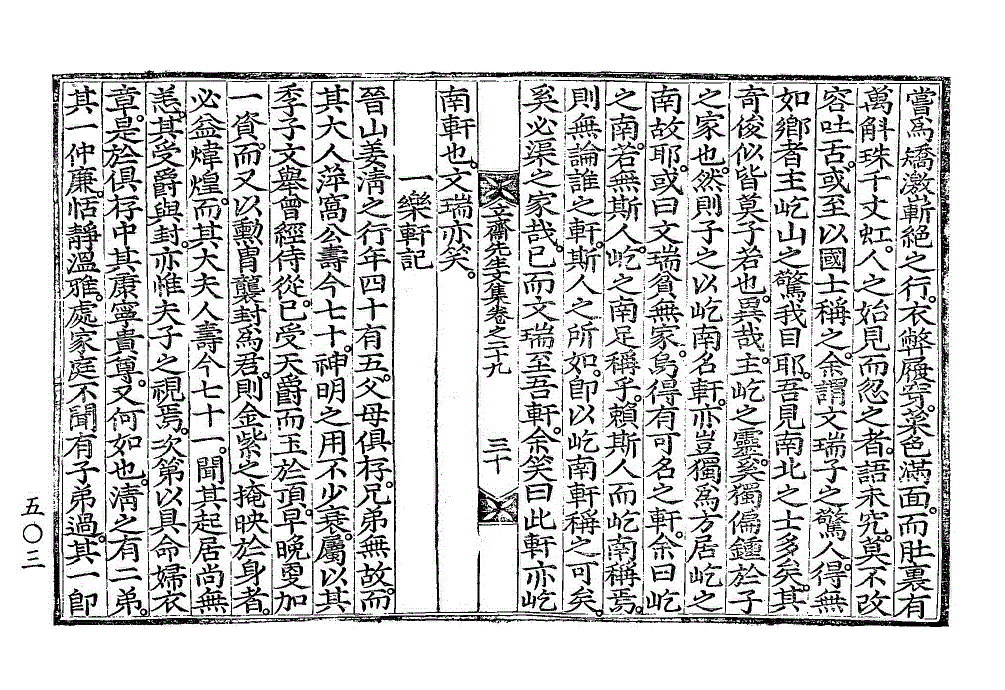 尝为矫激崭绝之行。衣弊履穿。菜色满面。而肚里有万斛珠千丈虹。人之始见而忽之者。语未究。莫不改容吐舌。或至以国士称之。余谓文瑞子之惊人。得无如乡者主屹山之惊我目耶。吾见南北之士多矣。其奇俊似皆莫子若也。异哉。主屹之灵。奚独偏钟于子之家也。然则子之以屹南名轩。亦岂独为方居屹之南故耶。或曰文瑞贫无家。乌得有可名之轩。余曰屹之南。若无斯人。屹之南足称乎。赖斯人而屹南称焉。则无论谁之轩。斯人之所如。即以屹南轩称之可矣。奚必渠之家哉。已而文瑞至吾轩。余笑曰此轩亦屹南轩也。文瑞亦笑。
尝为矫激崭绝之行。衣弊履穿。菜色满面。而肚里有万斛珠千丈虹。人之始见而忽之者。语未究。莫不改容吐舌。或至以国士称之。余谓文瑞子之惊人。得无如乡者主屹山之惊我目耶。吾见南北之士多矣。其奇俊似皆莫子若也。异哉。主屹之灵。奚独偏钟于子之家也。然则子之以屹南名轩。亦岂独为方居屹之南故耶。或曰文瑞贫无家。乌得有可名之轩。余曰屹之南。若无斯人。屹之南足称乎。赖斯人而屹南称焉。则无论谁之轩。斯人之所如。即以屹南轩称之可矣。奚必渠之家哉。已而文瑞至吾轩。余笑曰此轩亦屹南轩也。文瑞亦笑。一乐轩记
晋山姜清之行年四十有五。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而其大人萍窝公寿今七十。神明之用不少衰。属以其季子文举曾经侍从。已受天爵而玉于顶。早晚更加一资。而又以勋胄袭封为君。则金紫之掩映于身者。必益炜煌。而其大夫人寿今七十一。闻其起居尚无恙。其受爵与封。亦惟夫子之视焉。次第以具命妇衣章。是于俱存中其康宁贵尊。又何如也。清之有二弟。其一仲廉。恬静温雅。处家庭不闻有子弟过。其一即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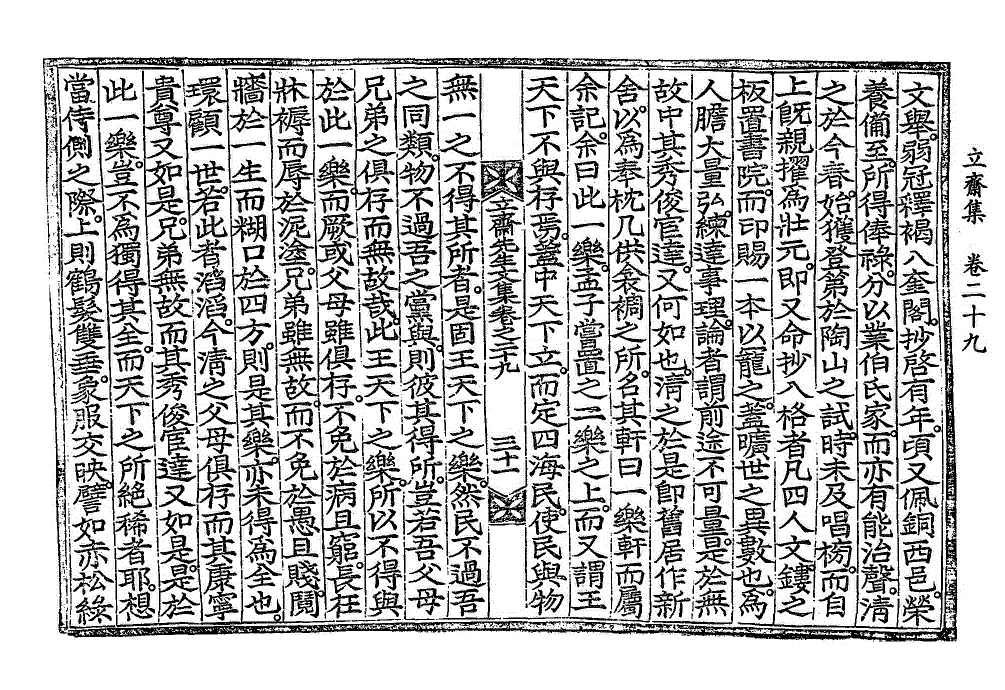 文举。弱冠释褐入奎阁。抄启有年。顷又佩铜西邑。荣养备至。所得俸禄。分以业伯氏家。而亦有能治声。清之于今春。始获登第于陶山之试。时未及唱榜。而自上既亲擢为壮元。即又命抄入格者凡四人文。镂之板置书院。而印赐一本以宠之。盖旷世之异数也。为人胆大量弘。练达事理。论者谓前途不可量。是于无故中其秀俊宦达。又何如也。清之于是即旧居作新舍。以为奉枕几供衾裯之所。名其轩曰一乐轩而属余记。余曰此一乐。孟子尝置之二乐之上。而又谓王天下不与存焉。盖中天下立。而定四海民。使民与物无一之不得其所者。是固王天下之乐。然民不过吾之同类。物不过吾之党与。则彼其得所。岂若吾父母兄弟之俱存而无故哉。此王天下之乐。所以不得与于此一乐。而厥或父母虽俱存。不免于病且穷。长在床褥而辱于泥涂。兄弟虽无故。而不免于愚且贱。阋墙于一生而糊口于四方。则是其乐。亦未得为全也。环顾一世。若此者滔滔。今清之父母俱存而其康宁贵尊又如是。兄弟无故而其秀俊宦达又如是。是于此一乐。岂不为独得其全。而天下之所绝稀者耶。想当侍侧之际。上则鹤发双垂。象服交映。譬如赤松绿
文举。弱冠释褐入奎阁。抄启有年。顷又佩铜西邑。荣养备至。所得俸禄。分以业伯氏家。而亦有能治声。清之于今春。始获登第于陶山之试。时未及唱榜。而自上既亲擢为壮元。即又命抄入格者凡四人文。镂之板置书院。而印赐一本以宠之。盖旷世之异数也。为人胆大量弘。练达事理。论者谓前途不可量。是于无故中其秀俊宦达。又何如也。清之于是即旧居作新舍。以为奉枕几供衾裯之所。名其轩曰一乐轩而属余记。余曰此一乐。孟子尝置之二乐之上。而又谓王天下不与存焉。盖中天下立。而定四海民。使民与物无一之不得其所者。是固王天下之乐。然民不过吾之同类。物不过吾之党与。则彼其得所。岂若吾父母兄弟之俱存而无故哉。此王天下之乐。所以不得与于此一乐。而厥或父母虽俱存。不免于病且穷。长在床褥而辱于泥涂。兄弟虽无故。而不免于愚且贱。阋墙于一生而糊口于四方。则是其乐。亦未得为全也。环顾一世。若此者滔滔。今清之父母俱存而其康宁贵尊又如是。兄弟无故而其秀俊宦达又如是。是于此一乐。岂不为独得其全。而天下之所绝稀者耶。想当侍侧之际。上则鹤发双垂。象服交映。譬如赤松绿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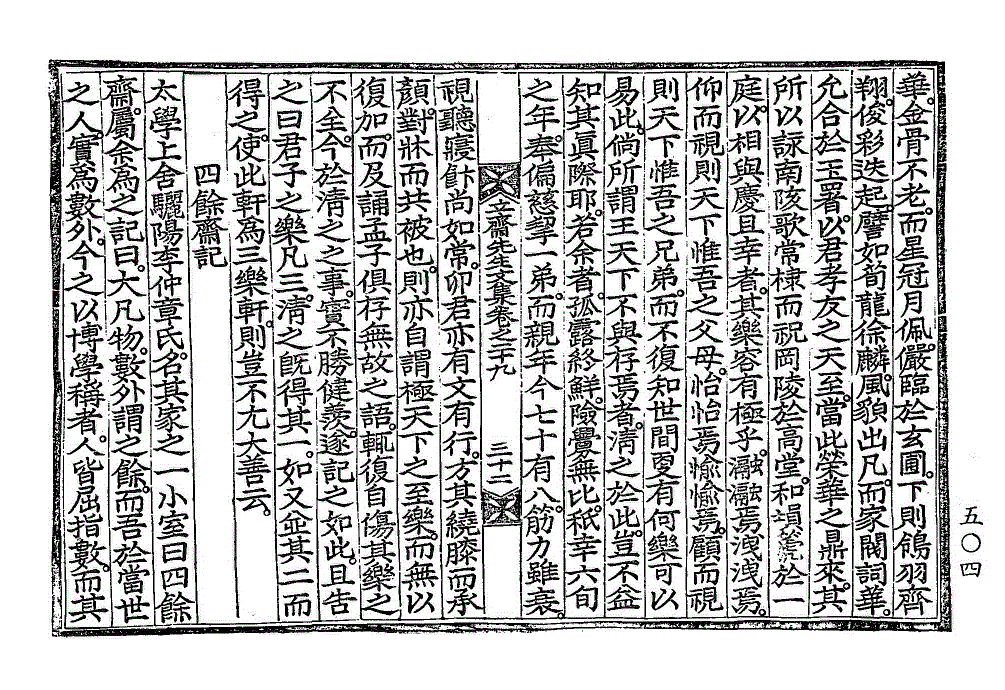 华。金骨不老。而星冠月佩。俨临于玄圃。下则鸰羽齐翔。俊彩迭起。譬如荀龙徐麟。风貌出凡。而家阀词华。允合于玉署。以君孝友之天至。当此荣华之鼎来。其所以咏南陔歌常棣而祝冈陵于高堂。和埙篪于一庭。以相与庆且幸者。其乐容有极乎。瀜瀜焉泄泄焉。仰而视则天下惟吾之父母。怡怡焉愉愉焉。顾而视则天下惟吾之兄弟。而不复知世间更有何乐可以易此。倘所谓王天下不与存焉者。清之于此。岂不益知其真际耶。若余者。孤露终鲜。险衅无比。秖幸六旬之年。奉偏慈挈一弟。而亲年今七十有八。筋力虽衰。视听寝饭尚如常。卯君亦有文有行。方其绕膝而承颜。对床而共被也。则亦自谓极天下之至乐。而无以复加。而及诵孟子俱存无故之语。辄复自伤其乐之不全。今于清之之事。实不胜健羡。遂记之如此。且告之曰君子之乐凡三。清之既得其一。如又并其二而得之。使此轩为三乐轩。则岂不尤大善云。
华。金骨不老。而星冠月佩。俨临于玄圃。下则鸰羽齐翔。俊彩迭起。譬如荀龙徐麟。风貌出凡。而家阀词华。允合于玉署。以君孝友之天至。当此荣华之鼎来。其所以咏南陔歌常棣而祝冈陵于高堂。和埙篪于一庭。以相与庆且幸者。其乐容有极乎。瀜瀜焉泄泄焉。仰而视则天下惟吾之父母。怡怡焉愉愉焉。顾而视则天下惟吾之兄弟。而不复知世间更有何乐可以易此。倘所谓王天下不与存焉者。清之于此。岂不益知其真际耶。若余者。孤露终鲜。险衅无比。秖幸六旬之年。奉偏慈挈一弟。而亲年今七十有八。筋力虽衰。视听寝饭尚如常。卯君亦有文有行。方其绕膝而承颜。对床而共被也。则亦自谓极天下之至乐。而无以复加。而及诵孟子俱存无故之语。辄复自伤其乐之不全。今于清之之事。实不胜健羡。遂记之如此。且告之曰君子之乐凡三。清之既得其一。如又并其二而得之。使此轩为三乐轩。则岂不尤大善云。四馀斋记
太学上舍骊阳李仲章氏。名其家之一小室曰四馀斋。属余为之记曰。大凡物。数外谓之馀。而吾于当世之人。实为数外。今之以博学称者。人皆屈指数。而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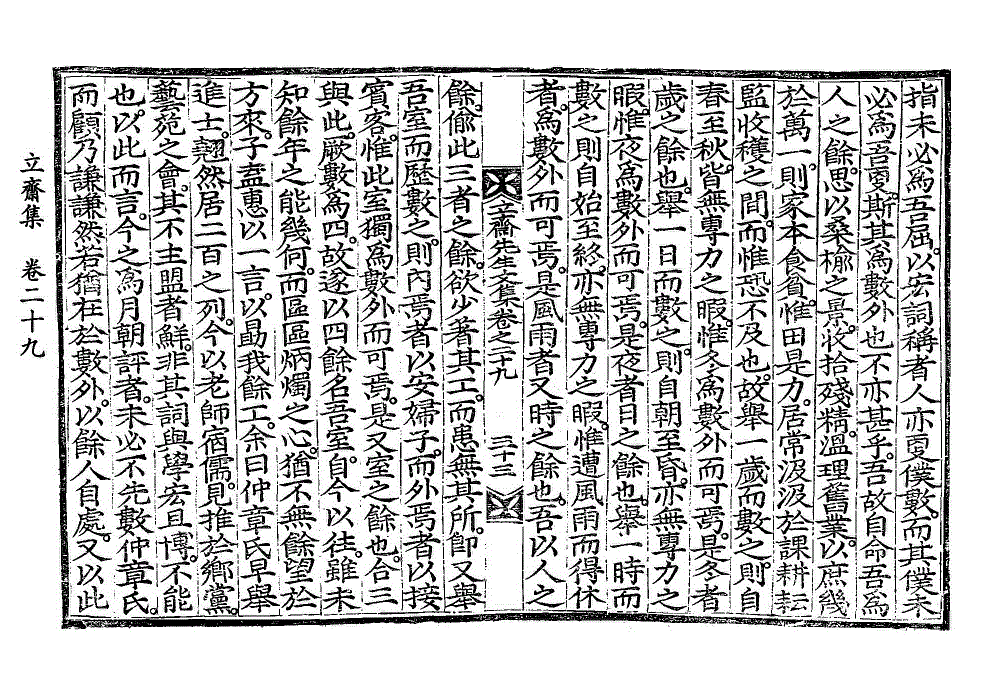 指未必为吾屈。以宏词称者人亦更仆数。而其仆未必为吾更。斯其为数外也不亦甚乎。吾故自命吾为人之馀。思以桑榆之景。收拾残精。温理旧业。以庶几于万一。则家本食贫。惟田是力。居常汲汲于课耕耘监收穫之间。而惟恐不及也。故举一岁而数之。则自春至秋。皆无专力之暇。惟冬为数外而可焉。是冬者岁之馀也。举一日而数之。则自朝至昏。亦无专力之暇。惟夜为数外而可焉。是夜者日之馀也。举一时而数之则自始至终。亦无专力之暇。惟遭风雨而得休者。为数外而可焉。是风雨者又时之馀也。吾以人之馀。偷此三者之馀。欲少著其工。而患无其所。即又举吾室而历数之。则内焉者以安妇子。而外焉者以接宾客。惟此室独为数外而可焉。是又室之馀也。合三与此。厥数为四。故遂以四馀名吾室。自今以往。虽未知馀年之能几何。而区区炳烛之心。犹不无馀望于方来。子盍惠以一言。以勖我馀工。余曰仲章氏早举进士。翘然居二百之列。今以老师宿儒。见推于乡党。艺苑之会。其不主盟者鲜。非其词与学宏且博。不能也。以此而言。今之为月朝评者。未必不先数仲章氏。而顾乃谦谦然若犹在于数外。以馀人自处。又以此
指未必为吾屈。以宏词称者人亦更仆数。而其仆未必为吾更。斯其为数外也不亦甚乎。吾故自命吾为人之馀。思以桑榆之景。收拾残精。温理旧业。以庶几于万一。则家本食贫。惟田是力。居常汲汲于课耕耘监收穫之间。而惟恐不及也。故举一岁而数之。则自春至秋。皆无专力之暇。惟冬为数外而可焉。是冬者岁之馀也。举一日而数之。则自朝至昏。亦无专力之暇。惟夜为数外而可焉。是夜者日之馀也。举一时而数之则自始至终。亦无专力之暇。惟遭风雨而得休者。为数外而可焉。是风雨者又时之馀也。吾以人之馀。偷此三者之馀。欲少著其工。而患无其所。即又举吾室而历数之。则内焉者以安妇子。而外焉者以接宾客。惟此室独为数外而可焉。是又室之馀也。合三与此。厥数为四。故遂以四馀名吾室。自今以往。虽未知馀年之能几何。而区区炳烛之心。犹不无馀望于方来。子盍惠以一言。以勖我馀工。余曰仲章氏早举进士。翘然居二百之列。今以老师宿儒。见推于乡党。艺苑之会。其不主盟者鲜。非其词与学宏且博。不能也。以此而言。今之为月朝评者。未必不先数仲章氏。而顾乃谦谦然若犹在于数外。以馀人自处。又以此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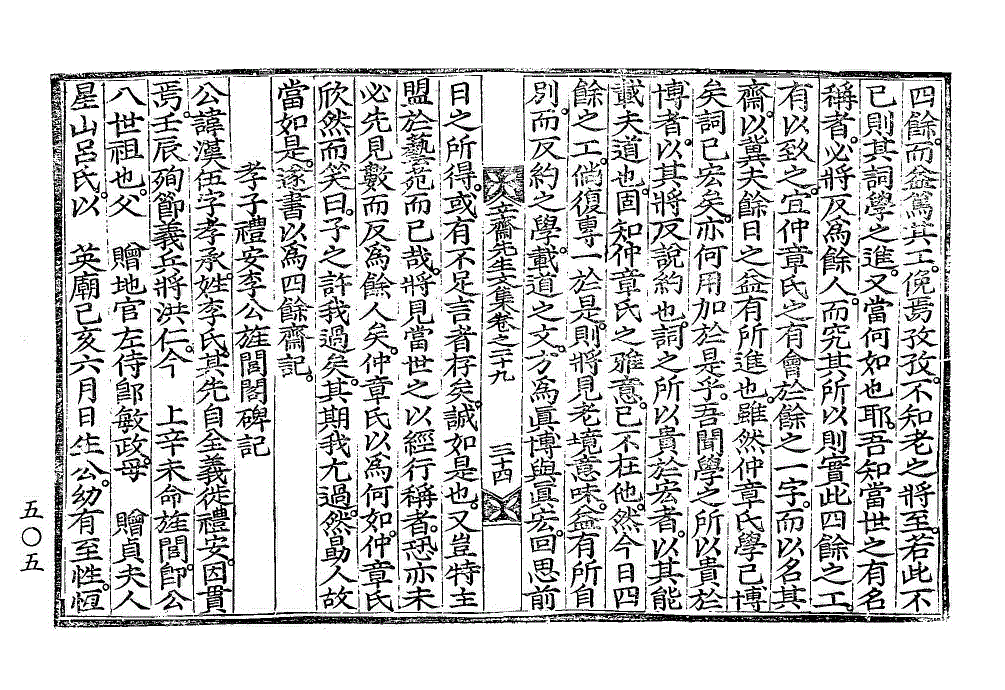 四馀。而益笃其工。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将至。若此不已则其词学之进。又当何如也耶。吾知当世之有名称者。必将反为馀人。而究其所以则实此四馀之工。有以致之。宜仲章氏之有会于馀之一字。而以名其斋。以冀夫馀日之益有所进也。虽然仲章氏学已博矣词已宏矣。亦何用加于是乎。吾闻学之所以贵于博者。以其将反说约也。词之所以贵于宏者。以其能载夫道也。固知仲章氏之雅意。已不在他。然今日四馀之工。倘复专一于是。则将见老境意味。益有所自别。而反约之学。载道之文。方为真博与真宏。回思前日之所得。或有不足言者存矣。诚如是也。又岂特主盟于艺苑而已哉。将见当世之以经行称者。恐亦未必先见数而反为馀人矣。仲章氏以为何如。仲章氏欣然而笑曰。子之许我过矣。其期我尤过。然勖人故当如是。遂书以为四馀斋记。
四馀。而益笃其工。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将至。若此不已则其词学之进。又当何如也耶。吾知当世之有名称者。必将反为馀人。而究其所以则实此四馀之工。有以致之。宜仲章氏之有会于馀之一字。而以名其斋。以冀夫馀日之益有所进也。虽然仲章氏学已博矣词已宏矣。亦何用加于是乎。吾闻学之所以贵于博者。以其将反说约也。词之所以贵于宏者。以其能载夫道也。固知仲章氏之雅意。已不在他。然今日四馀之工。倘复专一于是。则将见老境意味。益有所自别。而反约之学。载道之文。方为真博与真宏。回思前日之所得。或有不足言者存矣。诚如是也。又岂特主盟于艺苑而已哉。将见当世之以经行称者。恐亦未必先见数而反为馀人矣。仲章氏以为何如。仲章氏欣然而笑曰。子之许我过矣。其期我尤过。然勖人故当如是。遂书以为四馀斋记。孝子礼安李公旌闾阁碑记
公讳汉伍字孝承。姓李氏。其先自全义徙礼安。因贯焉。壬辰殉节义兵将洪仁。今 上辛未命旌闾。即公八世祖也。父 赠地官左侍郎敏政。母 赠贞夫人星山吕氏。以 英庙己亥六月日生公。幼有至性。恒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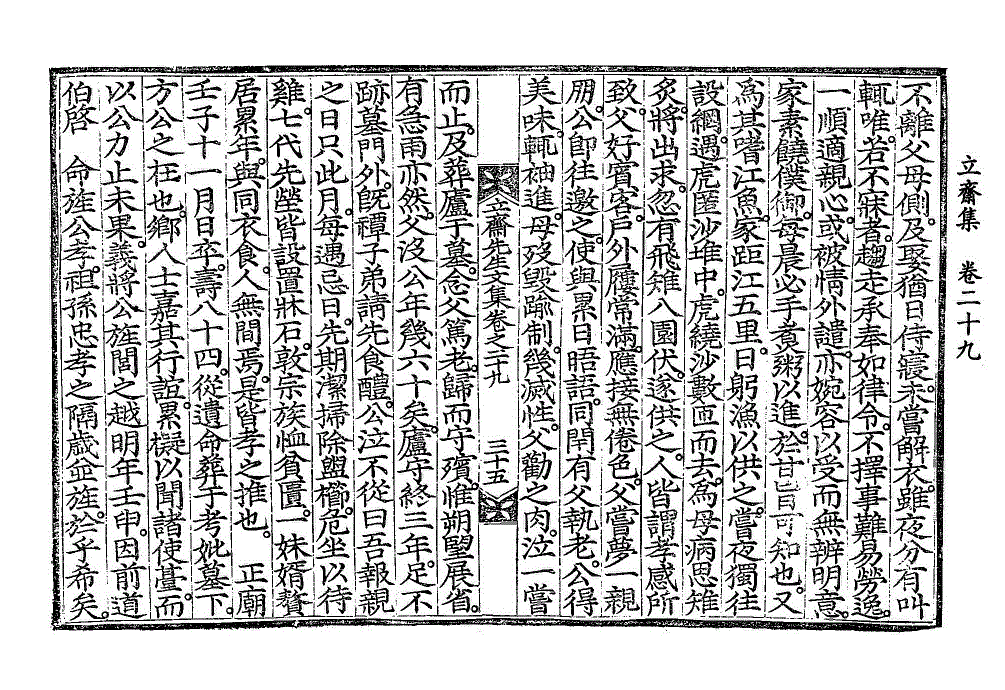 不离父母侧。及娶犹日侍寝。未尝解衣。虽夜分有叫辄唯。若不寐者。趋走承奉如律令。不择事难易劳逸。一顺适亲心。或被情外谴。亦婉容以受而无辨明意。家素饶仆御。每晨必手煮粥以进。于甘旨可知也。又为其嗜江鱼。家距江五里。日躬渔以供之。尝夜独往设网。遇虎匿沙堆中。虎绕沙数匝而去。为母病思雉炙。将出求。忽有飞雉入园伏。遂供之。人皆谓孝感所致。父好宾客。户外屦常满。应接无倦色。父尝梦一亲朋。公即往邀之。使与累日晤语。同闬有父执老。公得美味。辄袖进。母殁毁踰制。几灭性。父劝之肉。泣一尝而止。及葬庐于墓。念父笃老。归而守殡。惟朔望展省。有急雨亦然。父没公年几六十矣。庐守终三年。足不迹墓门外。既禫子弟请先食醴。公泣不从曰吾报亲之日只此月。每遇忌日。先期洁扫除盥栉。危坐以待鸡。七代先茔皆设置床石。敦宗族恤贫匮。一妹婿赘居累年。与同衣食。人无间焉。是皆孝之推也。 正庙壬子十一月日卒。寿八十四。从遗命葬于考妣墓下。方公之在也。乡人士嘉其行谊。累拟以闻诸使台。而以公力止未果。义将公旌闾之越明年壬申。因前道伯启 命旌公孝。祖孙忠孝之隔岁并旌。于乎希矣。
不离父母侧。及娶犹日侍寝。未尝解衣。虽夜分有叫辄唯。若不寐者。趋走承奉如律令。不择事难易劳逸。一顺适亲心。或被情外谴。亦婉容以受而无辨明意。家素饶仆御。每晨必手煮粥以进。于甘旨可知也。又为其嗜江鱼。家距江五里。日躬渔以供之。尝夜独往设网。遇虎匿沙堆中。虎绕沙数匝而去。为母病思雉炙。将出求。忽有飞雉入园伏。遂供之。人皆谓孝感所致。父好宾客。户外屦常满。应接无倦色。父尝梦一亲朋。公即往邀之。使与累日晤语。同闬有父执老。公得美味。辄袖进。母殁毁踰制。几灭性。父劝之肉。泣一尝而止。及葬庐于墓。念父笃老。归而守殡。惟朔望展省。有急雨亦然。父没公年几六十矣。庐守终三年。足不迹墓门外。既禫子弟请先食醴。公泣不从曰吾报亲之日只此月。每遇忌日。先期洁扫除盥栉。危坐以待鸡。七代先茔皆设置床石。敦宗族恤贫匮。一妹婿赘居累年。与同衣食。人无间焉。是皆孝之推也。 正庙壬子十一月日卒。寿八十四。从遗命葬于考妣墓下。方公之在也。乡人士嘉其行谊。累拟以闻诸使台。而以公力止未果。义将公旌闾之越明年壬申。因前道伯启 命旌公孝。祖孙忠孝之隔岁并旌。于乎希矣。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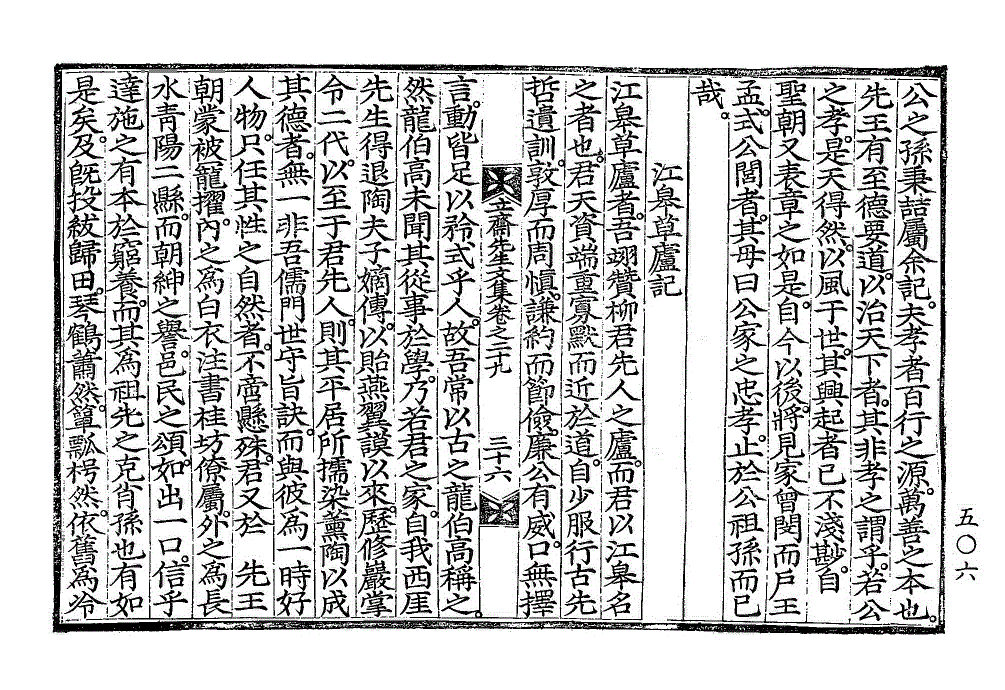 公之孙秉哲属余记。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治天下者。其非孝之谓乎。若公之孝。是天得然。以风于世。其兴起者已不浅鲜。自 圣朝又表章之如是。自今以后。将见家曾闵而户王孟。式公闾者。其母曰公家之忠孝。止于公祖孙而已哉。
公之孙秉哲属余记。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治天下者。其非孝之谓乎。若公之孝。是天得然。以风于世。其兴起者已不浅鲜。自 圣朝又表章之如是。自今以后。将见家曾闵而户王孟。式公闾者。其母曰公家之忠孝。止于公祖孙而已哉。江皋草庐记
江皋草庐者。吾翊赞柳君先人之庐。而君以江皋名之者也。君天资端重寡默而近于道。自少服行古先哲遗训。敦厚而周慎。谦约而节俭。廉公有威。口无择言。动皆足以矜式乎人。故吾常以古之龙伯高称之。然龙伯高未闻其从事于学。乃若君之家。自我西厓先生得退陶夫子嫡传。以贻燕翼谟以来。历修岩掌令二代。以至于君先人。则其平居所擩染薰陶以成其德者。无一非吾儒门世守旨诀。而与彼为一时好人物。只任其性之自然者。不啻悬殊。君又于 先王朝蒙被宠擢。内之为白衣注书桂坊僚属。外之为长水青阳二县。而朝绅之誉。邑民之颂。如出一口。信乎达施之有本于穷养。而其为祖先之克肖孙也有如是矣。及既投绂归田。琴鹤萧然。箪瓢枵然。依旧为冷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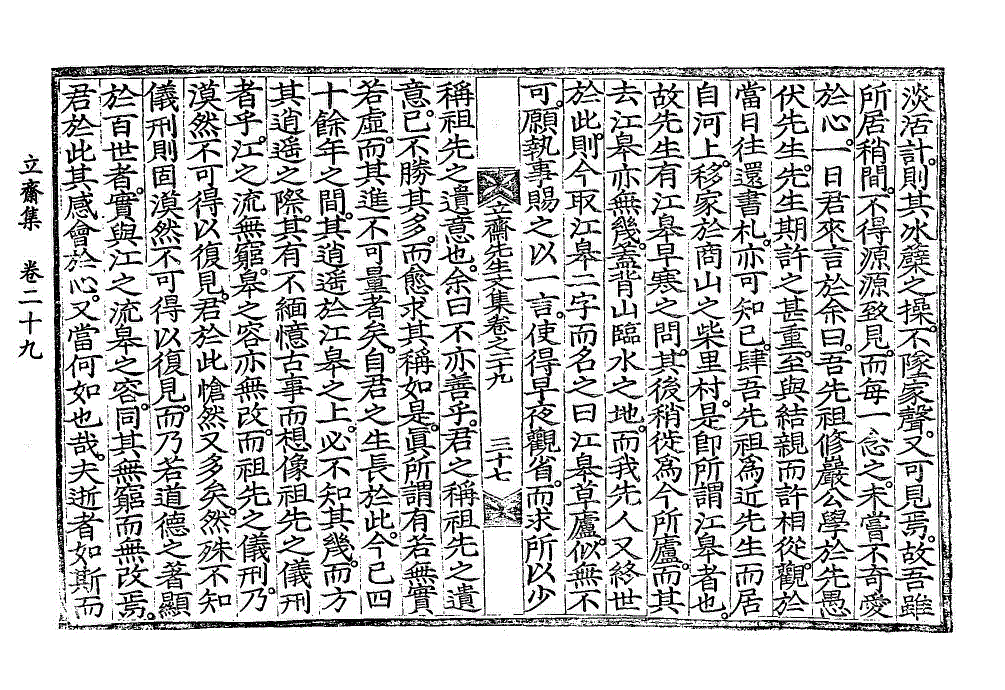 淡活计。则其冰檗之操。不坠家声。又可见焉。故吾虽所居稍间。不得源源致见。而每一念之。未尝不奇爱于心。一日君来言于余曰。吾先祖修岩公学于先愚伏先生。先生期许之甚重。至与结亲而许相从。观于当日往还书札。亦可知已。肆吾先祖为近先生而居自河上。移家于商山之柴里村。是即所谓江皋者也。故先生有江皋早寒之问。其后稍徙为今所庐。而其去江皋亦无几。盖背山临水之地。而我先人又终世于此。则今取江皋二字而名之曰江皋草庐。似无不可。愿执事赐之以一言。使得早夜观省。而求所以少称祖先之遗意也。余曰不亦善乎。君之称祖先之遗意。已不胜其多。而愈求其称如是。真所谓有若无实若虚。而其进不可量者矣。自君之生长于此。今已四十馀年之间。其逍遥于江皋之上。必不知其几。而方其逍遥之际。其有不缅忆古事而想像祖先之仪刑者乎。江之流无穷。皋之容亦无改。而祖先之仪刑。乃漠然不可得以复见。君于此怆然又多矣。然殊不知仪刑则固漠然不可得以复见。而乃若道德之著显于百世者。实与江之流皋之容。同其无穷而无改焉。君于此其感会于心。又当何如也哉。夫逝者如斯而
淡活计。则其冰檗之操。不坠家声。又可见焉。故吾虽所居稍间。不得源源致见。而每一念之。未尝不奇爱于心。一日君来言于余曰。吾先祖修岩公学于先愚伏先生。先生期许之甚重。至与结亲而许相从。观于当日往还书札。亦可知已。肆吾先祖为近先生而居自河上。移家于商山之柴里村。是即所谓江皋者也。故先生有江皋早寒之问。其后稍徙为今所庐。而其去江皋亦无几。盖背山临水之地。而我先人又终世于此。则今取江皋二字而名之曰江皋草庐。似无不可。愿执事赐之以一言。使得早夜观省。而求所以少称祖先之遗意也。余曰不亦善乎。君之称祖先之遗意。已不胜其多。而愈求其称如是。真所谓有若无实若虚。而其进不可量者矣。自君之生长于此。今已四十馀年之间。其逍遥于江皋之上。必不知其几。而方其逍遥之际。其有不缅忆古事而想像祖先之仪刑者乎。江之流无穷。皋之容亦无改。而祖先之仪刑。乃漠然不可得以复见。君于此怆然又多矣。然殊不知仪刑则固漠然不可得以复见。而乃若道德之著显于百世者。实与江之流皋之容。同其无穷而无改焉。君于此其感会于心。又当何如也哉。夫逝者如斯而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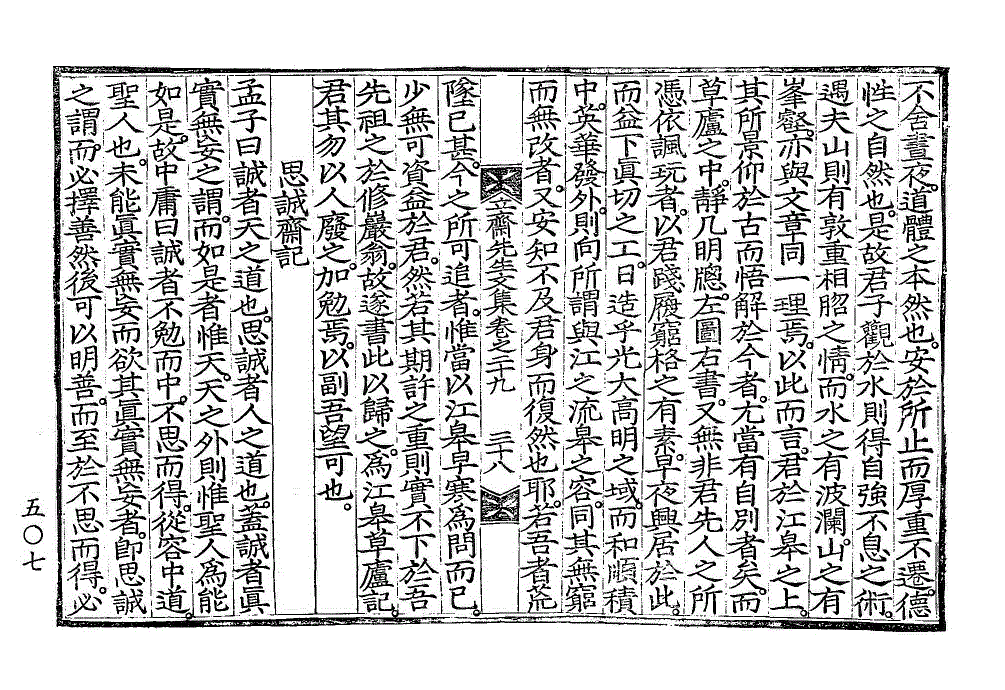 不舍昼夜。道体之本然也。安于所止而厚重不迁。德性之自然也。是故君子观于水则得自强不息之术。遇夫山则有敦重相吻之情。而水之有波澜。山之有峰壑。亦与文章同一理焉。以此而言。君于江皋之上。其所景仰于古而悟解于今者。尤当有自别者矣。而草庐之中。静几明窗。左图右书。又无非君先人之所凭依讽玩者。以君践履穷格之有素。早夜兴居于此。而益下真切之工。日造乎光大高明之域。而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则向所谓与江之流皋之容。同其无穷而无改者。又安知不及君身而复然也耶。若吾者荒坠已甚。今之所可追者。惟当以江皋早寒为问而已。少无可资益于君。然若其期许之重则实不下于吾先祖之于修岩翁。故遂书此以归之。为江皋草庐记。君其勿以人废之。加勉焉。以副吾望可也。
不舍昼夜。道体之本然也。安于所止而厚重不迁。德性之自然也。是故君子观于水则得自强不息之术。遇夫山则有敦重相吻之情。而水之有波澜。山之有峰壑。亦与文章同一理焉。以此而言。君于江皋之上。其所景仰于古而悟解于今者。尤当有自别者矣。而草庐之中。静几明窗。左图右书。又无非君先人之所凭依讽玩者。以君践履穷格之有素。早夜兴居于此。而益下真切之工。日造乎光大高明之域。而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则向所谓与江之流皋之容。同其无穷而无改者。又安知不及君身而复然也耶。若吾者荒坠已甚。今之所可追者。惟当以江皋早寒为问而已。少无可资益于君。然若其期许之重则实不下于吾先祖之于修岩翁。故遂书此以归之。为江皋草庐记。君其勿以人废之。加勉焉。以副吾望可也。思诚斋记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盖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而如是者惟天。天之外则惟圣人为能如是。故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者。即思诚之谓。而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而至于不思而得。必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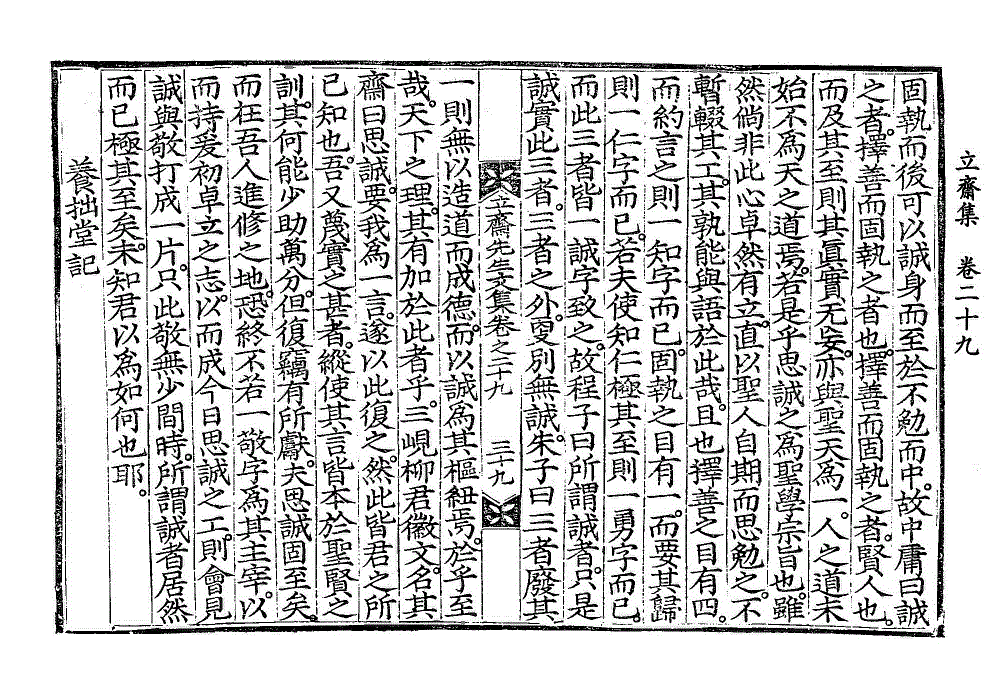 固执而后可以诚身而至于不勉而中。故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而固执之者。贤人也。而及其至则其真实无妄。亦与圣天为一。人之道未始不为天之道焉。若是乎思诚之为圣学宗旨也。虽然倘非此心卓然有立。直以圣人自期而思勉之。不暂辍其工。其孰能与语于此哉。且也择善之目有四。而约言之则一知字而已。固执之目有一。而要其归则一仁字而已。若夫使知仁极其至则一勇字而已。而此三者皆一诚字致之。故程子曰所谓诚者。只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朱子曰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而以诚为其枢纽焉。于乎至哉。天下之理。其有加于此者乎。三岘柳君徽文。名其斋曰思诚。要我为一言。遂以此复之。然此皆君之所已知也。吾又蔑实之甚者。纵使其言皆本于圣贤之训。其何能少助万分。但复窃有所献。夫思诚固至矣。而在吾人进修之地。恐终不若一敬字为其主宰。以而持爰初卓立之志。以而成今日思诚之工。则会见诚与敬打成一片。只此敬无少间时。所谓诚者居然而已极其至矣。未知君以为如何也耶。
固执而后可以诚身而至于不勉而中。故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而固执之者。贤人也。而及其至则其真实无妄。亦与圣天为一。人之道未始不为天之道焉。若是乎思诚之为圣学宗旨也。虽然倘非此心卓然有立。直以圣人自期而思勉之。不暂辍其工。其孰能与语于此哉。且也择善之目有四。而约言之则一知字而已。固执之目有一。而要其归则一仁字而已。若夫使知仁极其至则一勇字而已。而此三者皆一诚字致之。故程子曰所谓诚者。只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朱子曰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而以诚为其枢纽焉。于乎至哉。天下之理。其有加于此者乎。三岘柳君徽文。名其斋曰思诚。要我为一言。遂以此复之。然此皆君之所已知也。吾又蔑实之甚者。纵使其言皆本于圣贤之训。其何能少助万分。但复窃有所献。夫思诚固至矣。而在吾人进修之地。恐终不若一敬字为其主宰。以而持爰初卓立之志。以而成今日思诚之工。则会见诚与敬打成一片。只此敬无少间时。所谓诚者居然而已极其至矣。未知君以为如何也耶。养拙堂记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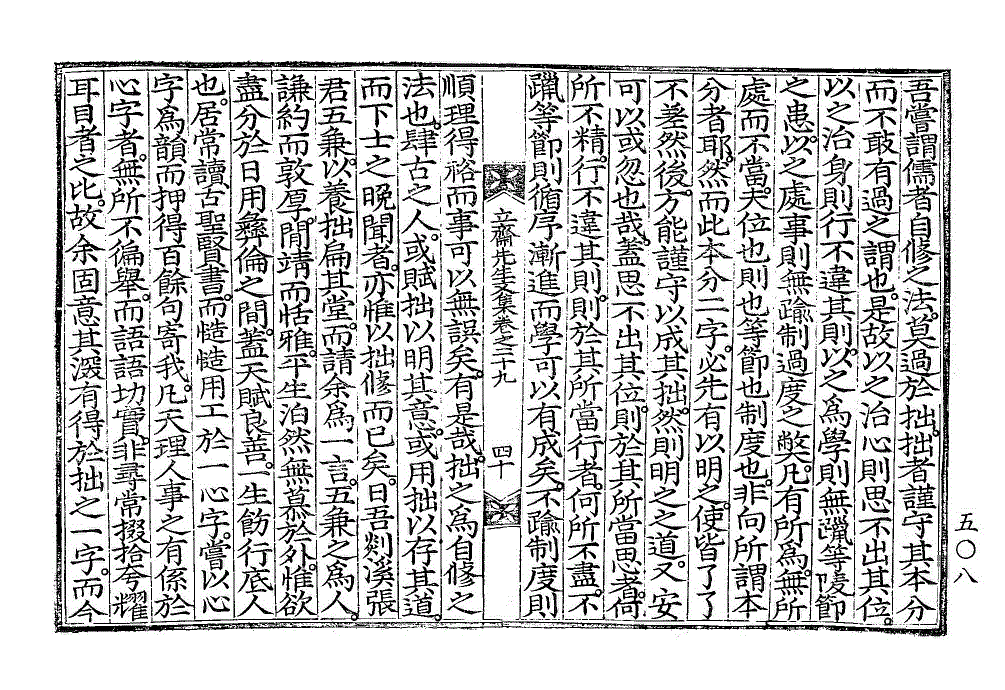 吾尝谓儒者自修之法。莫过于拙。拙者谨守其本分而不敢有过之谓也。是故以之治心则思不出其位。以之治身则行不违其则。以之为学则无躐等陵节之患。以之处事则无踰制过度之弊。凡有所为。无所处而不当。夫位也则也等节也制度也。非向所谓本分者耶。然而此本分二字。必先有以明之。使皆了了不差然后。方能谨守以成其拙。然则明之之道。又安可以或忽也哉。盖思不出其位。则于其所当思者。何所不精。行不违其则。则于其所当行者。何所不尽。不躐等节则循序渐进而学可以有成矣。不踰制度则顺理得裕而事可以无误矣。有是哉。拙之为自修之法也。肆古之人。或赋拙以明其意。或用拙以存其道。而下士之晚闻者。亦惟以拙修而已矣。日吾剡溪张君五兼。以养拙扁其堂。而请余为一言。五兼之为人。谦约而敦厚。閒靖而恬雅。平生泊然无慕于外。惟欲尽分于日用彝伦之间。盖天赋良善。一生饬行底人也。居常读古圣贤书。而慥慥用工于一心字。尝以心字为韵而押得百馀句寄我。凡天理人事之有系于心字者。无所不遍举。而语语切实。非寻常掇拾夸耀耳目者之比。故余固意其深有得于拙之一字。而今
吾尝谓儒者自修之法。莫过于拙。拙者谨守其本分而不敢有过之谓也。是故以之治心则思不出其位。以之治身则行不违其则。以之为学则无躐等陵节之患。以之处事则无踰制过度之弊。凡有所为。无所处而不当。夫位也则也等节也制度也。非向所谓本分者耶。然而此本分二字。必先有以明之。使皆了了不差然后。方能谨守以成其拙。然则明之之道。又安可以或忽也哉。盖思不出其位。则于其所当思者。何所不精。行不违其则。则于其所当行者。何所不尽。不躐等节则循序渐进而学可以有成矣。不踰制度则顺理得裕而事可以无误矣。有是哉。拙之为自修之法也。肆古之人。或赋拙以明其意。或用拙以存其道。而下士之晚闻者。亦惟以拙修而已矣。日吾剡溪张君五兼。以养拙扁其堂。而请余为一言。五兼之为人。谦约而敦厚。閒靖而恬雅。平生泊然无慕于外。惟欲尽分于日用彝伦之间。盖天赋良善。一生饬行底人也。居常读古圣贤书。而慥慥用工于一心字。尝以心字为韵而押得百馀句寄我。凡天理人事之有系于心字者。无所不遍举。而语语切实。非寻常掇拾夸耀耳目者之比。故余固意其深有得于拙之一字。而今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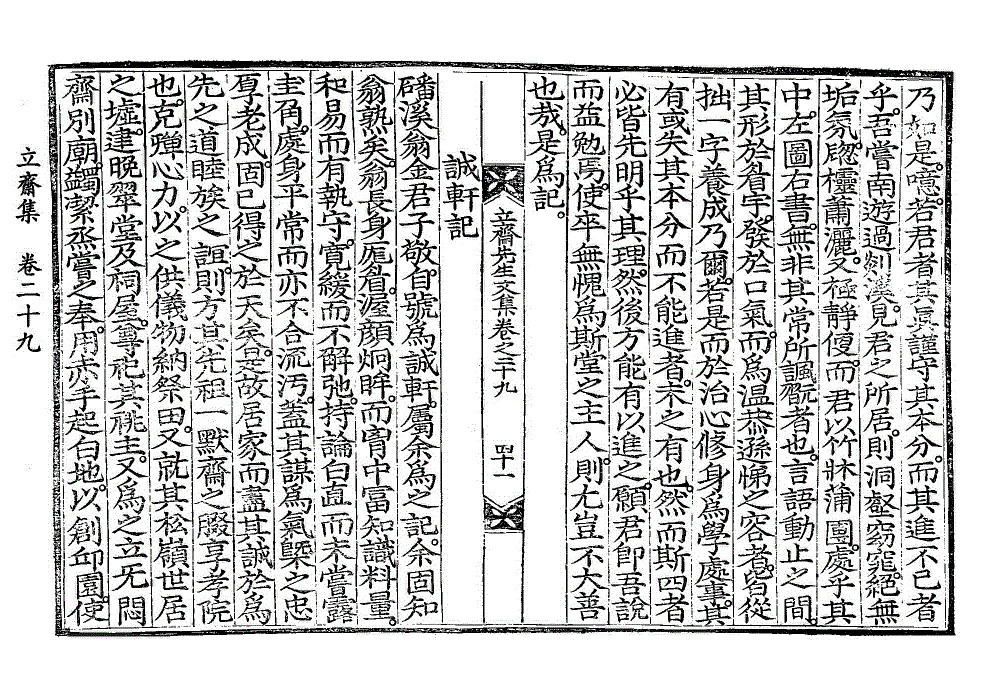 乃如是。噫。若君者其真谨守其本分。而其进不已者乎。吾尝南游过剡溪。见君之所居。则洞壑窈窕。绝无垢氛。窗棂萧洒。又极静便。而君以竹床蒲团。处乎其中。左图右书。无非其常所讽玩者也。言语动止之间。其形于眉宇。发于口气。而为温恭逊悌之容者。皆从拙一字养成乃尔。若是而于治心修身为学处事。其有或失其本分而不能进者。未之有也。然而斯四者必皆先明乎其理。然后方能有以进之。愿君即吾说而益勉焉。使卒无愧为斯堂之主人。则尤岂不大善也哉。是为记。
乃如是。噫。若君者其真谨守其本分。而其进不已者乎。吾尝南游过剡溪。见君之所居。则洞壑窈窕。绝无垢氛。窗棂萧洒。又极静便。而君以竹床蒲团。处乎其中。左图右书。无非其常所讽玩者也。言语动止之间。其形于眉宇。发于口气。而为温恭逊悌之容者。皆从拙一字养成乃尔。若是而于治心修身为学处事。其有或失其本分而不能进者。未之有也。然而斯四者必皆先明乎其理。然后方能有以进之。愿君即吾说而益勉焉。使卒无愧为斯堂之主人。则尤岂不大善也哉。是为记。诚轩记
磻溪翁金君子敬。自号为诚轩。属余为之记。余固知翁熟矣。翁长身厖眉。渥颜炯眸。而胸中富知识料量。和易而有执守。宽缓而不解弛。持论白直而未尝露圭角。处身平常而亦不合流污。盖其谋为气槩之忠厚老成。固已得之于天矣。是故居家而尽其诚于为先之道睦族之谊。则方其先祖一默斋之啜享孝院也。克殚心力。以之供仪物纳祭田。又就其松岭世居之墟。建晚翠堂及祠屋。尊祀其祧主。又为之立无闷斋别庙。蠲洁烝尝之奉。用赤手起白地。以创丘园。使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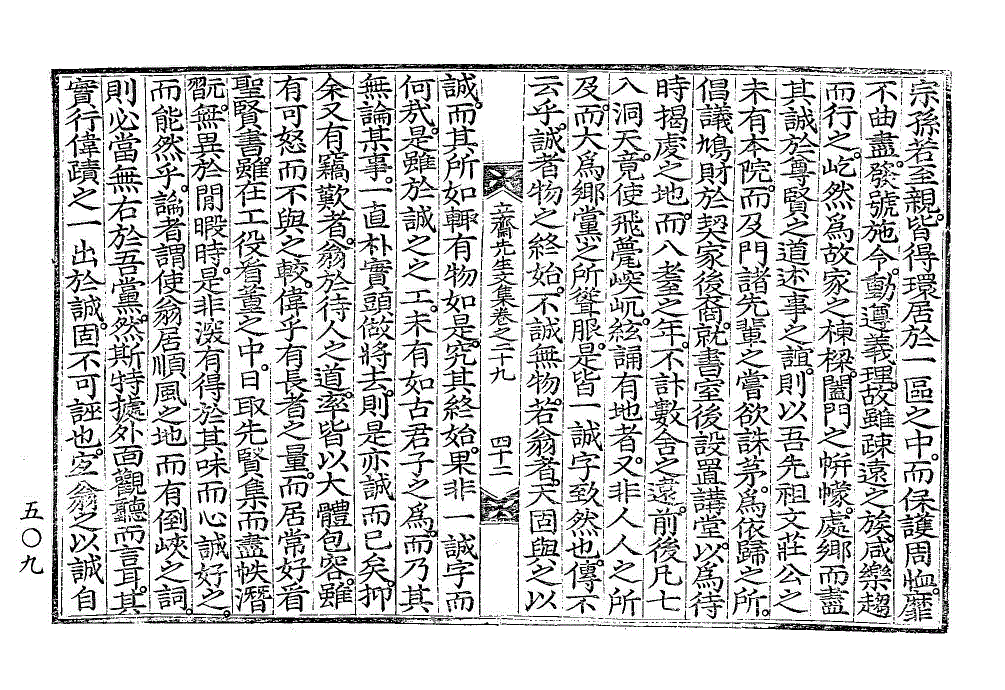 宗孙若至亲。皆得环居于一区之中。而保护周恤。靡不曲尽。发号施令。动遵义理。故虽疏远之族。咸乐趋而行之。屹然为故家之栋梁。阖门之帲幪。处乡而尽其诚于尊贤之道述事之谊。则以吾先祖文庄公之未有本院。而及门诸先辈之尝欲诛茅。为依归之所。倡议鸠财于契家后裔。就书室后设置讲堂。以为待时揭虔之地。而八耋之年。不计数舍之远。前后凡七入洞天。竟使飞甍㟮屼。弦诵有地者。又非人人之所及。而大为乡党之所耸服。是皆一诚字致然也。传不云乎。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若翁者。天固与之以诚。而其所如辄有物如是。究其终始。果非一诚字而何哉。是虽于诚之之工。未有如古君子之为。而乃其无论某事。一直朴实头做将去。则是亦诚而已矣。抑余又有窃叹者。翁于待人之道。率皆以大体包容。虽有可怒而不与之较。伟乎有长者之量。而居常好看圣贤书。虽在工役看董之中。日取先贤集而尽帙潜玩。无异于閒暇时。是非深有得于其味而心诚好之。而能然乎。论者谓使翁居顺风之地而有倒峡之词。则必当无右于吾党。然斯特据外面观听而言耳。其实行伟迹之一出于诚。固不可诬也。宜翁之以诚自
宗孙若至亲。皆得环居于一区之中。而保护周恤。靡不曲尽。发号施令。动遵义理。故虽疏远之族。咸乐趋而行之。屹然为故家之栋梁。阖门之帲幪。处乡而尽其诚于尊贤之道述事之谊。则以吾先祖文庄公之未有本院。而及门诸先辈之尝欲诛茅。为依归之所。倡议鸠财于契家后裔。就书室后设置讲堂。以为待时揭虔之地。而八耋之年。不计数舍之远。前后凡七入洞天。竟使飞甍㟮屼。弦诵有地者。又非人人之所及。而大为乡党之所耸服。是皆一诚字致然也。传不云乎。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若翁者。天固与之以诚。而其所如辄有物如是。究其终始。果非一诚字而何哉。是虽于诚之之工。未有如古君子之为。而乃其无论某事。一直朴实头做将去。则是亦诚而已矣。抑余又有窃叹者。翁于待人之道。率皆以大体包容。虽有可怒而不与之较。伟乎有长者之量。而居常好看圣贤书。虽在工役看董之中。日取先贤集而尽帙潜玩。无异于閒暇时。是非深有得于其味而心诚好之。而能然乎。论者谓使翁居顺风之地而有倒峡之词。则必当无右于吾党。然斯特据外面观听而言耳。其实行伟迹之一出于诚。固不可诬也。宜翁之以诚自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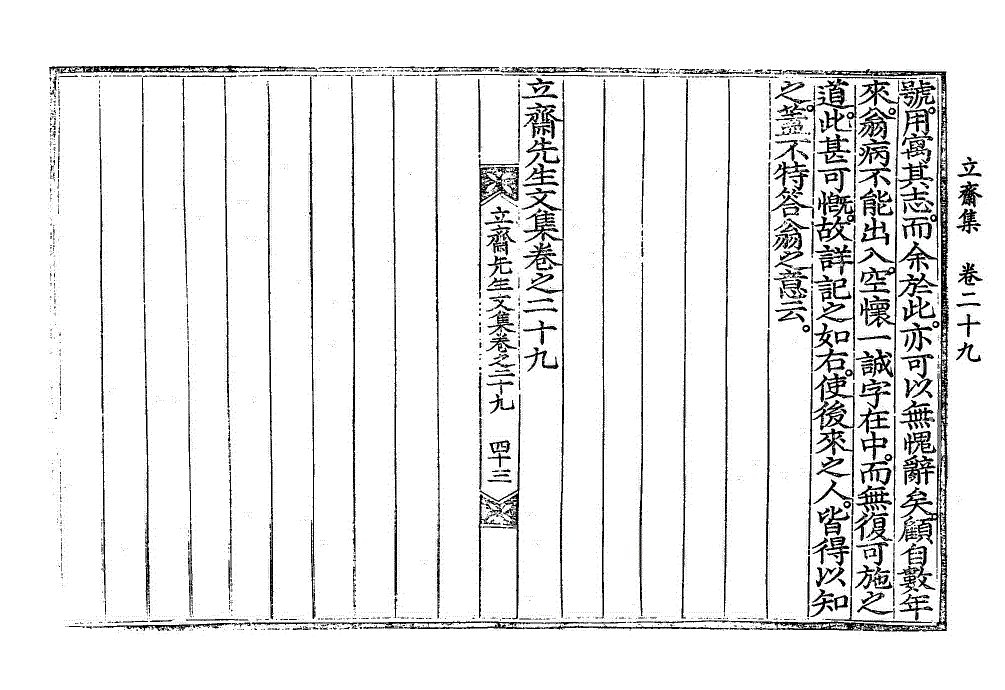 号。用寓其志。而余于此。亦可以无愧辞矣。顾自数年来。翁病不能出入。空怀一诚字在中。而无复可施之道。此甚可慨。故详记之如右。使后来之人。皆得以知之。盖不特答翁之意云。
号。用寓其志。而余于此。亦可以无愧辞矣。顾自数年来。翁病不能出入。空怀一诚字在中。而无复可施之道。此甚可慨。故详记之如右。使后来之人。皆得以知之。盖不特答翁之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