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x 页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书
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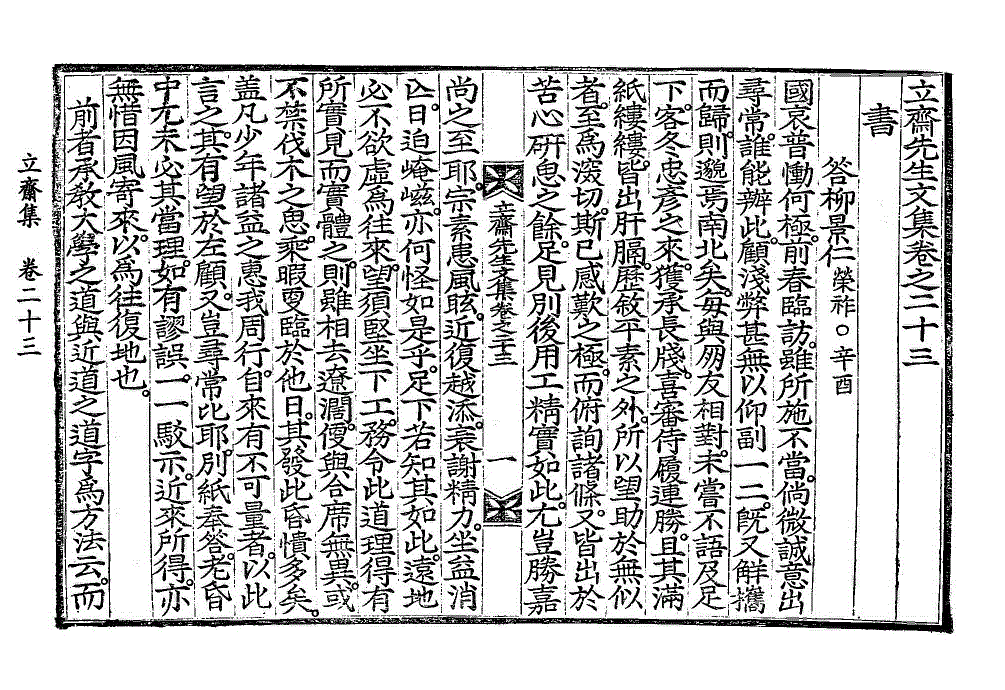 答柳景仁(荣祚○辛酉)
答柳景仁(荣祚○辛酉)国哀普恸何极。前春临访。虽所施不当。倘微诚意出寻常。谁能办此。顾浅弊甚无以仰副一二。既又解携而归。则邈焉南北矣。每与朋友相对。未尝不语及足下。客冬忠彦之来。获承长笺。喜审侍履连胜。且其满纸缕缕。皆出肝膈。历叙平素之外。所以望助于无似者。至为深切。斯已感叹之极。而俯询诸条。又皆出于苦心研思之馀。足见别后用工精实如此。尤岂胜嘉尚之至耶。宗素患风眩。近复越添。衰谢精力。坐益消亡。日迫崦嵫。亦何怪如是乎。足下若知其如此。远地必不欲虚为往来。望须坚坐下工。务令此道理得有所实见而实体之。则虽相去辽阔。便与合席无异。或不禁伐木之思。乘暇更临于他日。其发此昏愦多矣。盖凡少年诸益之惠我周行。自来有不可量者。以此言之。其有望于左顾。又岂寻常比耶。别纸奉答。老昏中尤未必其当理。如有谬误。一一驳示。近来所得。亦无惜因风寄来。以为往复地也。
前者承教大学之道与近道之道字为方法云。而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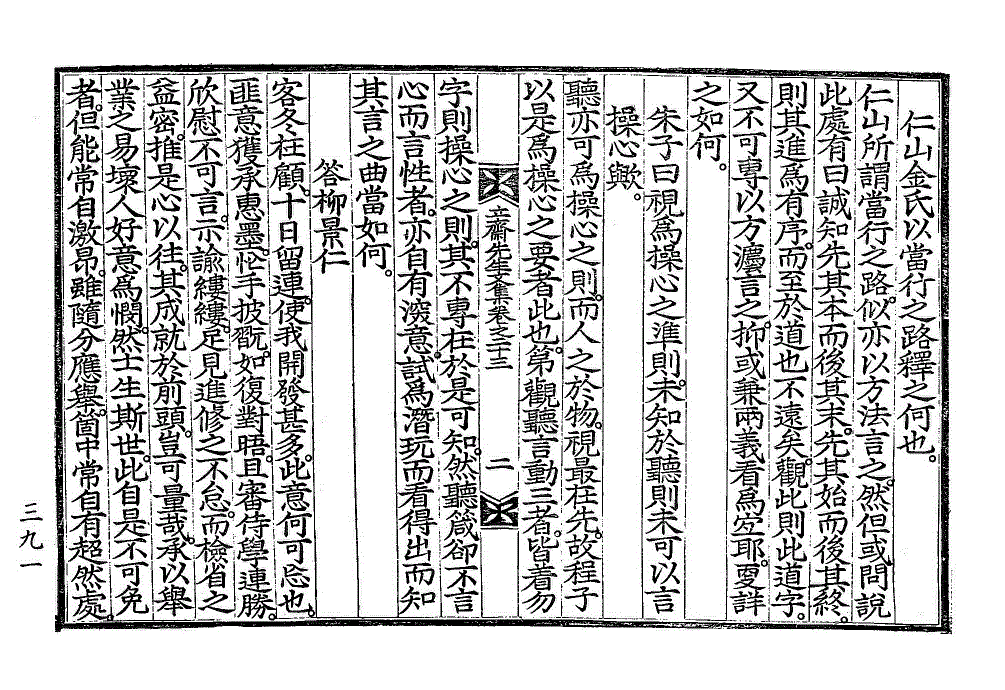 仁山金氏以当行之路释之何也。
仁山金氏以当行之路释之何也。仁山所谓当行之路。似亦以方法言之。然但或问说此处有曰诚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终。则其进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远矣。观此则此道字。又不可专以方法言之。抑或兼两义看为宜耶。更详之如何。
朱子曰视为操心之准则。未知于听则未可以言操心欤。
听亦可为操心之则。而人之于物。视最在先。故程子以是为操心之要者此也。第观听言动三者。皆着勿字则操心之则。其不专在于是可知。然听箴却不言心而言性者。亦自有深意。试为潜玩而看得出而知其言之曲当如何。
答柳景仁
客冬枉顾。十日留连。使我开发甚多。此意何可忘也。匪意获承惠墨。忙手披玩。如复对晤。且审侍学连胜。欣慰不可言。示谕缕缕。足见进修之不怠。而检省之益密。推是心以往。其成就于前头。岂可量哉。承以举业之易坏人好意为悯。然士生斯世。此自是不可免者。但能常自激昂。虽随分应举。个中常自有超然处。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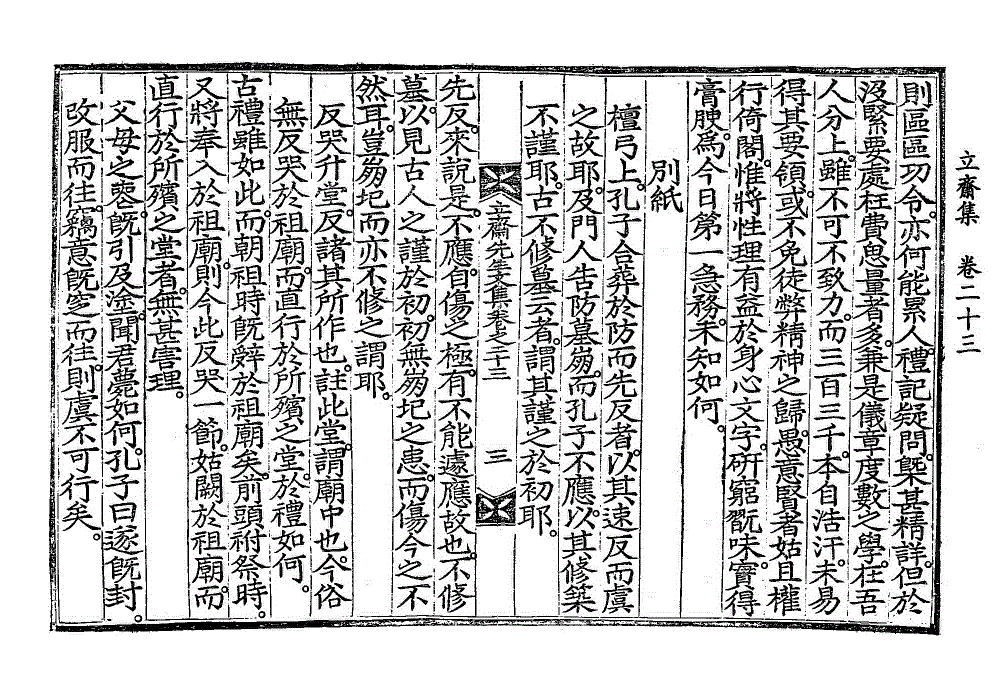 则区区功令。亦何能累人。礼记疑问。槩甚精详。但于没紧要处枉费思量者多。兼是仪章度数之学。在吾人分上。虽不可不致力。而三百三千。本自浩汗。未易得其要领。或不免徒弊精神之归。愚意贤者姑且权行倚阁。惟将性理有益于身心文字。研穷玩味。实得膏腴。为今日第一急务。未知如何。
则区区功令。亦何能累人。礼记疑问。槩甚精详。但于没紧要处枉费思量者多。兼是仪章度数之学。在吾人分上。虽不可不致力。而三百三千。本自浩汗。未易得其要领。或不免徒弊精神之归。愚意贤者姑且权行倚阁。惟将性理有益于身心文字。研穷玩味。实得膏腴。为今日第一急务。未知如何。别纸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而先反者。以其速反而虞之故耶。及门人告防墓崩。而孔子不应。以其修筑不谨耶。古不修墓云者。谓其谨之于初耶。
先反。来说是。不应。自伤之极。有不能遽应故也。不修墓。以见古人之谨于初。初无崩圮之患。而伤今之不然耳。岂崩圮而亦不修之谓耶。
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注此堂。谓庙中也。今俗无反哭于祖庙。而直行于所殡之堂。于礼如何。
古礼虽如此。而朝祖时既辞于祖庙矣。前头祔祭时。又将奉入于祖庙。则今此反哭一节。姑阙于祖庙。而直行于所殡之堂者。无甚害理。
父母之丧。既引及涂。闻君薨如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窃意既窆而往。则虞不可行矣。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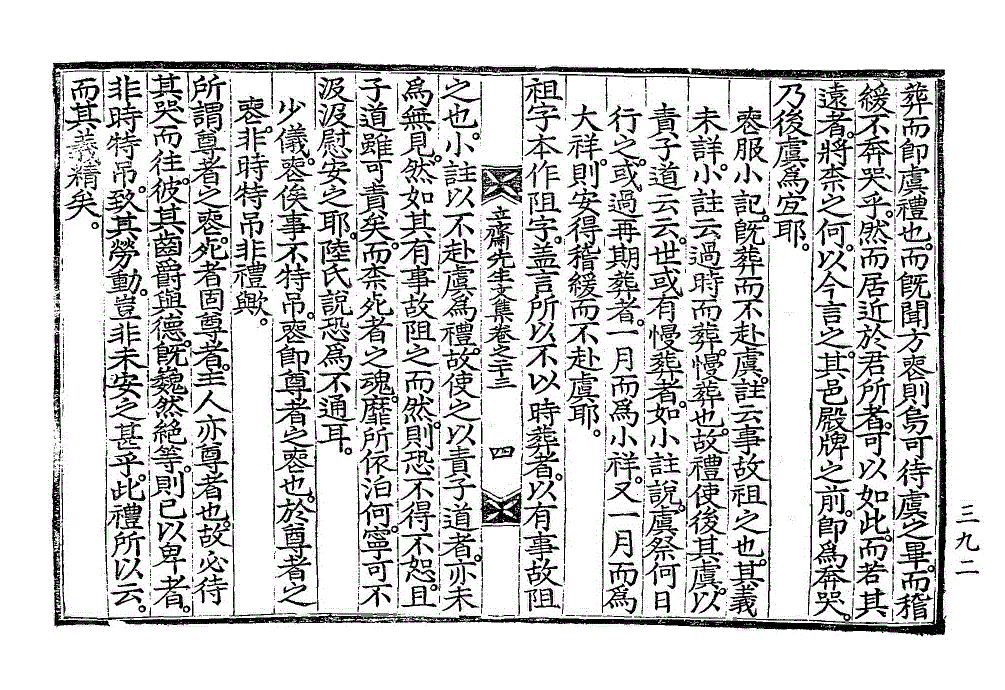 葬而即虞礼也。而既闻方丧则乌可待虞之毕。而稽缓不奔哭乎。然而居近于君所者。可以如此。而若其远者。将柰之何。以今言之。其邑殿牌之前。即为奔哭。乃后虞为宜耶。
葬而即虞礼也。而既闻方丧则乌可待虞之毕。而稽缓不奔哭乎。然而居近于君所者。可以如此。而若其远者。将柰之何。以今言之。其邑殿牌之前。即为奔哭。乃后虞为宜耶。丧服小记。既葬而不赴虞。注云事故祖之也。其义未详。小注云过时而葬。慢葬也。故礼使后其虞。以责子道云云。世或有慢葬者。如小注说。虞祭何日行之。或过再期葬者。一月而为小祥。又一月而为大祥。则安得稽缓而不赴虞耶。
祖字本作阻字。盖言所以不以时葬者。以有事故阻之也。小注以不赴虞为礼。故使之以责子道者。亦未为无见。然如其有事故阻之而然。则恐不得不恕。且子道虽可责矣。而柰死者之魂。靡所依泊何。宁可不汲汲慰安之耶。陆氏说恐为不通耳。
少仪。丧俟事不特吊。丧即尊者之丧也。于尊者之丧。非时特吊非礼欤。
所谓尊者之丧。死者固尊者。主人亦尊者也。故必待其哭而往。彼其齿爵与德。既巍然绝等。则己以卑者。非时特吊。致其劳动。岂非未安之甚乎。此礼所以云。而其义精矣。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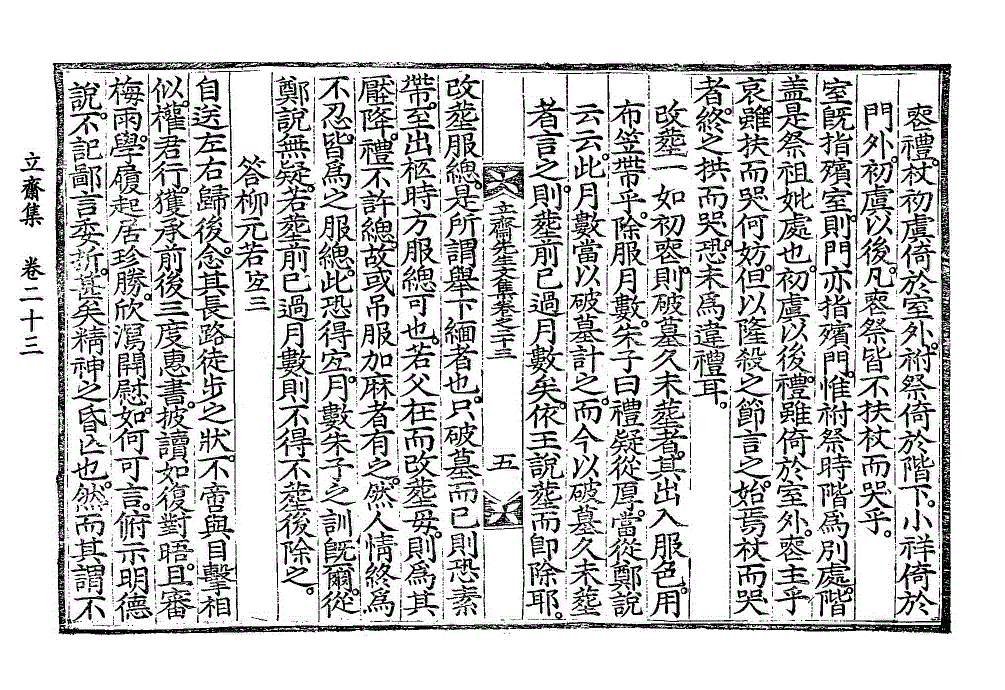 丧礼。杖初虞倚于室外。祔祭倚于阶下。小祥倚于门外。初虞以后。凡丧祭皆不扶杖而哭乎。
丧礼。杖初虞倚于室外。祔祭倚于阶下。小祥倚于门外。初虞以后。凡丧祭皆不扶杖而哭乎。室既指殡室。则门亦指殡门。惟祔祭时阶为别处。阶盖是祭祖妣处也。初虞以后。礼虽倚于室外。丧主乎哀。虽扶而哭何妨。但以隆杀之节言之。始焉杖而哭者。终之拱而哭。恐未为违礼耳。
改葬一如初丧。则破墓久未葬者。其出入服色。用布笠带乎。除服月数。朱子曰礼疑从厚。当从郑说云云。此月数当以破墓计之。而今以破墓久未葬者言之。则葬前已过月数矣。依王说葬而即除耶。
改葬服缌。是所谓举下缅者也。只破墓而已则恐素带。至出柩时方服缌可也。若父在而改葬母。则为其压降。礼不许缌。故或吊服加麻者有之。然人情终为不忍。皆为之服缌。此恐得宜。月数朱子之训既尔。从郑说无疑。若葬前已过月数则不得不葬后除之。
答柳元若(宜三)
自送左右归后。念其长路徒步之状。不啻与目击相似。权君行。获承前后三度惠书。披读如复对晤。且审梅雨。学履起居珍胜。欣泻开慰。如何可言。俯示明德说。不记鄙言委折。甚矣精神之昏亡也。然而其谓不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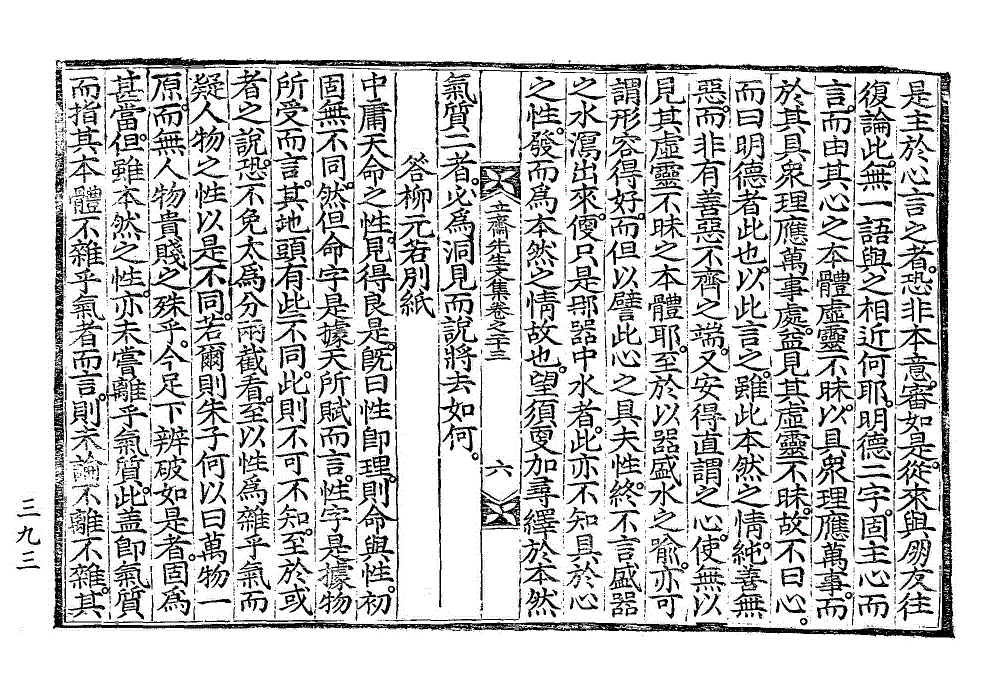 是主于心言之者。恐非本意。审如是。从来与朋友往复论此。无一语与之相近何耶。明德二字。固主心而言。而由其心之本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而于其具众理应万事处。益见其虚灵不昧。故不曰心。而曰明德者此也。以此言之。虽此本然之情。纯善无恶。而非有善恶不齐之端。又安得直谓之心。使无以见其虚灵不昧之本体耶。至于以器盛水之喻。亦可谓形容得好。而但以譬此心之具夫性。终不言盛器之水泻出来。便只是那器中水者。此亦不知具于心之性。发而为本然之情故也。望须更加寻绎于本然气质二者。必为洞见而说将去如何。
是主于心言之者。恐非本意。审如是。从来与朋友往复论此。无一语与之相近何耶。明德二字。固主心而言。而由其心之本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而于其具众理应万事处。益见其虚灵不昧。故不曰心。而曰明德者此也。以此言之。虽此本然之情。纯善无恶。而非有善恶不齐之端。又安得直谓之心。使无以见其虚灵不昧之本体耶。至于以器盛水之喻。亦可谓形容得好。而但以譬此心之具夫性。终不言盛器之水泻出来。便只是那器中水者。此亦不知具于心之性。发而为本然之情故也。望须更加寻绎于本然气质二者。必为洞见而说将去如何。答柳元若别纸
中庸天命之性。见得良是。既曰性即理。则命与性。初固无不同。然但命字是据天所赋而言。性字是据物所受而言。其地头有些不同。此则不可不知。至于或者之说。恐不免太为分两截看。至以性为杂乎气而疑人物之性以是不同。若尔则朱子何以曰万物一原。而无人物贵贱之殊乎。今足下辨破如是者。固为甚当。但虽本然之性。亦未尝离乎气质。此盖即气质而指其本体不杂乎气者而言。则未论不离不杂。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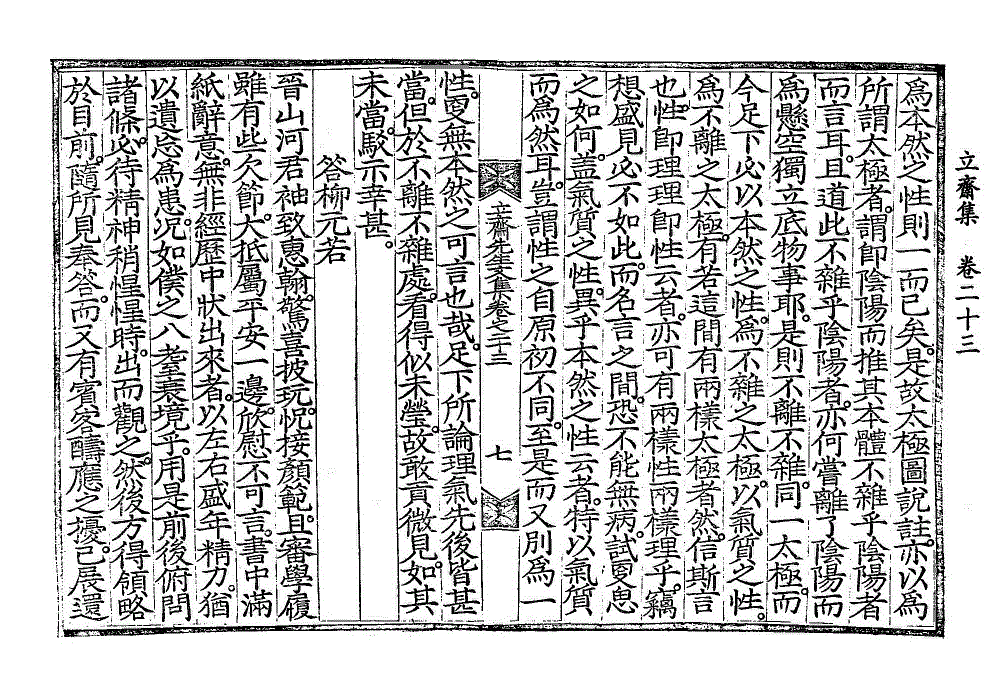 为本然之性则一而已矣。是故太极图说注。亦以为所谓太极者。谓即阴阳而推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者而言耳。且道此不杂乎阴阳者。亦何尝离了阴阳而为县空独立底物事耶。是则不离不杂。同一太极。而今足下必以本然之性。为不杂之太极。以气质之性。为不离之太极。有若这间有两样太极者然。信斯言也。性即理理即性云者。亦可有两样性两样理乎。窃想盛见必不如此。而名言之间。恐不能无病。试更思之如何。盖气质之性。异乎本然之性云者。特以气质而为然耳。岂谓性之自原初不同。至是而又别为一性。更无本然之可言也哉。足下所论理气先后皆甚当。但于不离不杂处。看得似未莹。故敢贡微见。如其未当。驳示幸甚。
为本然之性则一而已矣。是故太极图说注。亦以为所谓太极者。谓即阴阳而推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者而言耳。且道此不杂乎阴阳者。亦何尝离了阴阳而为县空独立底物事耶。是则不离不杂。同一太极。而今足下必以本然之性。为不杂之太极。以气质之性。为不离之太极。有若这间有两样太极者然。信斯言也。性即理理即性云者。亦可有两样性两样理乎。窃想盛见必不如此。而名言之间。恐不能无病。试更思之如何。盖气质之性。异乎本然之性云者。特以气质而为然耳。岂谓性之自原初不同。至是而又别为一性。更无本然之可言也哉。足下所论理气先后皆甚当。但于不离不杂处。看得似未莹。故敢贡微见。如其未当。驳示幸甚。答柳元若
晋山河君袖致惠翰。惊喜披玩。恍接颜范。且审学履虽有些欠节。大抵属平安一边。欣慰不可言。书中满纸辞意。无非经历中状出来者。以左右盛年精力。犹以遗忘为患。况如仆之八耋衰境乎。用是前后俯问诸条。必待精神稍惺惺时。出而观之。然后方得领略于目前。随所见奉答。而又有宾客酬应之扰。已展还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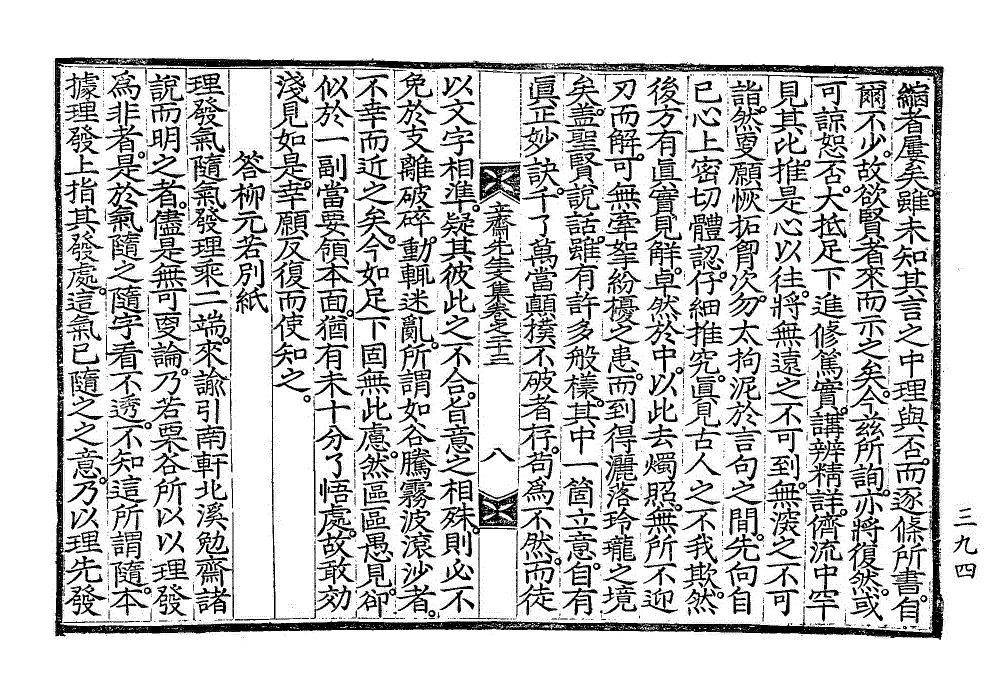 缩者屡矣。虽未知其言之中理与否。而逐条所书。自尔不少。故欲贤者来而示之矣。今玆所询。亦将复然。或可谅恕否。大抵足下进修笃实。讲辨精详。侪流中罕见其比。推是心以往。将无远之不可到。无深之不可诣。然更愿恢拓胸次。勿太拘泥于言句之间。先向自己心上密切体认。仔细推究。真见古人之不我欺。然后方有真实见解。卓然于中。以此去烛照。无所不迎刃而解。可无牵挐纷扰之患。而到得洒落玲珑之境矣。盖圣贤说话。虽有许多般样。其中一个立意。自有真正妙诀。千了万当颠扑不破者存。苟为不然。而徒以文字相准。疑其彼此之不合。旨意之相殊。则必不免于支离破碎。动辄迷乱。所谓如谷腾雾波滚沙者。不幸而近之矣。今如足下固无此虑。然区区愚见。却似于一副当要领本面。犹有未十分了悟处。故敢效浅见如是。幸愿反复而使知之。
缩者屡矣。虽未知其言之中理与否。而逐条所书。自尔不少。故欲贤者来而示之矣。今玆所询。亦将复然。或可谅恕否。大抵足下进修笃实。讲辨精详。侪流中罕见其比。推是心以往。将无远之不可到。无深之不可诣。然更愿恢拓胸次。勿太拘泥于言句之间。先向自己心上密切体认。仔细推究。真见古人之不我欺。然后方有真实见解。卓然于中。以此去烛照。无所不迎刃而解。可无牵挐纷扰之患。而到得洒落玲珑之境矣。盖圣贤说话。虽有许多般样。其中一个立意。自有真正妙诀。千了万当颠扑不破者存。苟为不然。而徒以文字相准。疑其彼此之不合。旨意之相殊。则必不免于支离破碎。动辄迷乱。所谓如谷腾雾波滚沙者。不幸而近之矣。今如足下固无此虑。然区区愚见。却似于一副当要领本面。犹有未十分了悟处。故敢效浅见如是。幸愿反复而使知之。答柳元若别纸
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二端。来谕引南轩北溪勉斋诸说而明之者。尽是无可更论。乃若栗谷所以以理发为非者。是于气随之随字看不透。不知这所谓随。本据理发上指其发处。这气已随之之意。乃以理先发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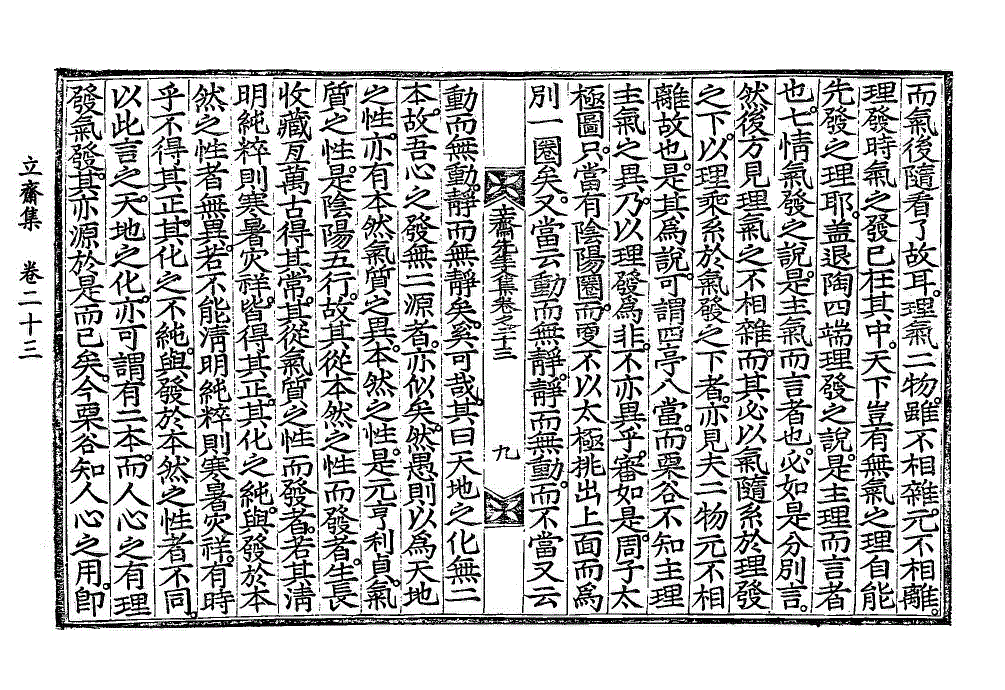 而气后随看了故耳。理气二物。虽不相杂。元不相离。理发时气之发已在其中。天下岂有无气之理自能先发之理耶。盖退陶四端理发之说。是主理而言者也。七情气发之说。是主气而言者也。必如是分别言。然后方见理气之不相杂。而其必以气随系于理发之下。以理乘系于气发之下者。亦见夫二物元不相离故也。是其为说。可谓四亭八当。而栗谷不知主理主气之异。乃以理发为非。不亦异乎。审如是。周子太极图。只当有阴阳圈。而更不以太极挑出上面而为别一圈矣。又当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而不当又云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矣。奚可哉。其曰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源者。亦似矣。然愚则以为天地之性。亦有本然气质之异。本然之性。是元亨利贞。气质之性。是阴阳五行。故其从本然之性而发者。生长收藏亘万古得其常。其从气质之性而发者。若其清明纯粹则寒暑灾祥。皆得其正。其化之纯。与发于本然之性者无异。若不能清明纯粹则寒暑灾祥。有时乎不得其正。其化之不纯。与发于本然之性者不同。以此言之。天地之化。亦可谓有二本。而人心之有理发气发。其亦源于是而已矣。今栗谷知人心之用。即
而气后随看了故耳。理气二物。虽不相杂。元不相离。理发时气之发已在其中。天下岂有无气之理自能先发之理耶。盖退陶四端理发之说。是主理而言者也。七情气发之说。是主气而言者也。必如是分别言。然后方见理气之不相杂。而其必以气随系于理发之下。以理乘系于气发之下者。亦见夫二物元不相离故也。是其为说。可谓四亭八当。而栗谷不知主理主气之异。乃以理发为非。不亦异乎。审如是。周子太极图。只当有阴阳圈。而更不以太极挑出上面而为别一圈矣。又当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而不当又云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矣。奚可哉。其曰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源者。亦似矣。然愚则以为天地之性。亦有本然气质之异。本然之性。是元亨利贞。气质之性。是阴阳五行。故其从本然之性而发者。生长收藏亘万古得其常。其从气质之性而发者。若其清明纯粹则寒暑灾祥。皆得其正。其化之纯。与发于本然之性者无异。若不能清明纯粹则寒暑灾祥。有时乎不得其正。其化之不纯。与发于本然之性者不同。以此言之。天地之化。亦可谓有二本。而人心之有理发气发。其亦源于是而已矣。今栗谷知人心之用。即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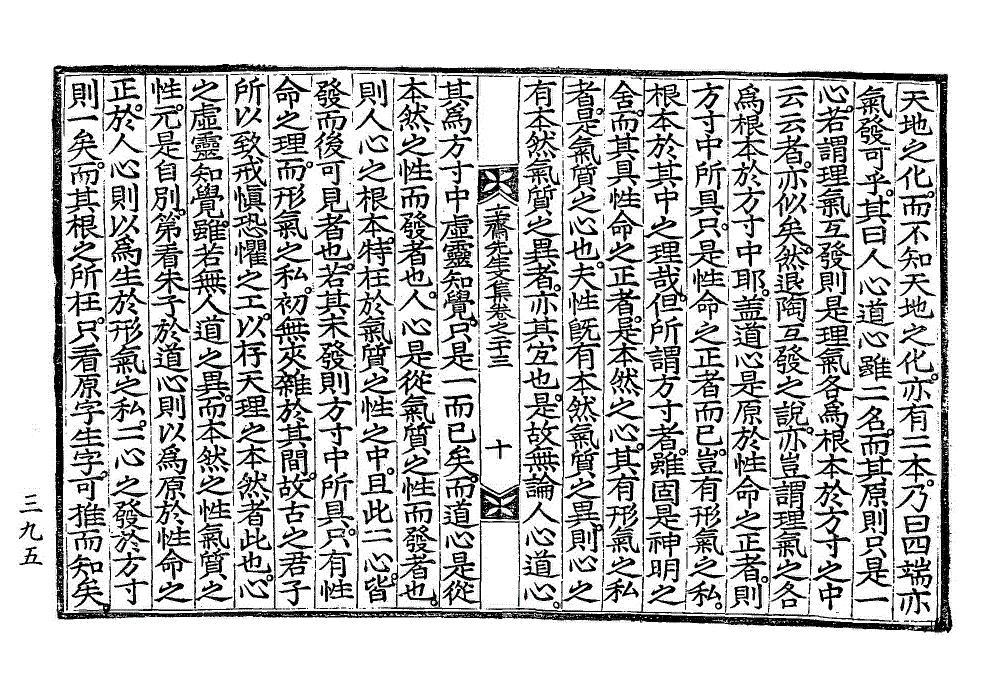 天地之化。而不知天地之化。亦有二本。乃曰四端亦气发可乎。其曰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是一心。若谓理气互发则是理气各为根本于方寸之中云云者。亦似矣。然退陶互发之说。亦岂谓理气之各为根本于方寸中耶。盖道心是原于性命之正者。则方寸中所具。只是性命之正者而已。岂有形气之私。根本于其中之理哉。但所谓方寸者。虽固是神明之舍。而其具性命之正者。是本然之心。其有形气之私者。是气质之心也。夫性既有本然气质之异。则心之有本然气质之异者。亦其宜也。是故无论人心道心。其为方寸中虚灵知觉。只是一而已矣。而道心是从本然之性而发者也。人心是从气质之性而发者也。则人心之根本。特在于气质之性之中。且此二心。皆发而后可见者也。若其未发则方寸中所具。只有性命之理。而形气之私。初无夹杂于其间。故古之君子所以致戒慎恐惧之工。以存天理之本然者此也。心之虚灵知觉。虽若无人道之异。而本然之性气质之性。元是自别。第看朱子于道心则以为原于性命之正。于人心则以为生于形气之私。二心之发于方寸则一矣。而其根之所在。只看原字生字。可推而知矣。
天地之化。而不知天地之化。亦有二本。乃曰四端亦气发可乎。其曰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是一心。若谓理气互发则是理气各为根本于方寸之中云云者。亦似矣。然退陶互发之说。亦岂谓理气之各为根本于方寸中耶。盖道心是原于性命之正者。则方寸中所具。只是性命之正者而已。岂有形气之私。根本于其中之理哉。但所谓方寸者。虽固是神明之舍。而其具性命之正者。是本然之心。其有形气之私者。是气质之心也。夫性既有本然气质之异。则心之有本然气质之异者。亦其宜也。是故无论人心道心。其为方寸中虚灵知觉。只是一而已矣。而道心是从本然之性而发者也。人心是从气质之性而发者也。则人心之根本。特在于气质之性之中。且此二心。皆发而后可见者也。若其未发则方寸中所具。只有性命之理。而形气之私。初无夹杂于其间。故古之君子所以致戒慎恐惧之工。以存天理之本然者此也。心之虚灵知觉。虽若无人道之异。而本然之性气质之性。元是自别。第看朱子于道心则以为原于性命之正。于人心则以为生于形气之私。二心之发于方寸则一矣。而其根之所在。只看原字生字。可推而知矣。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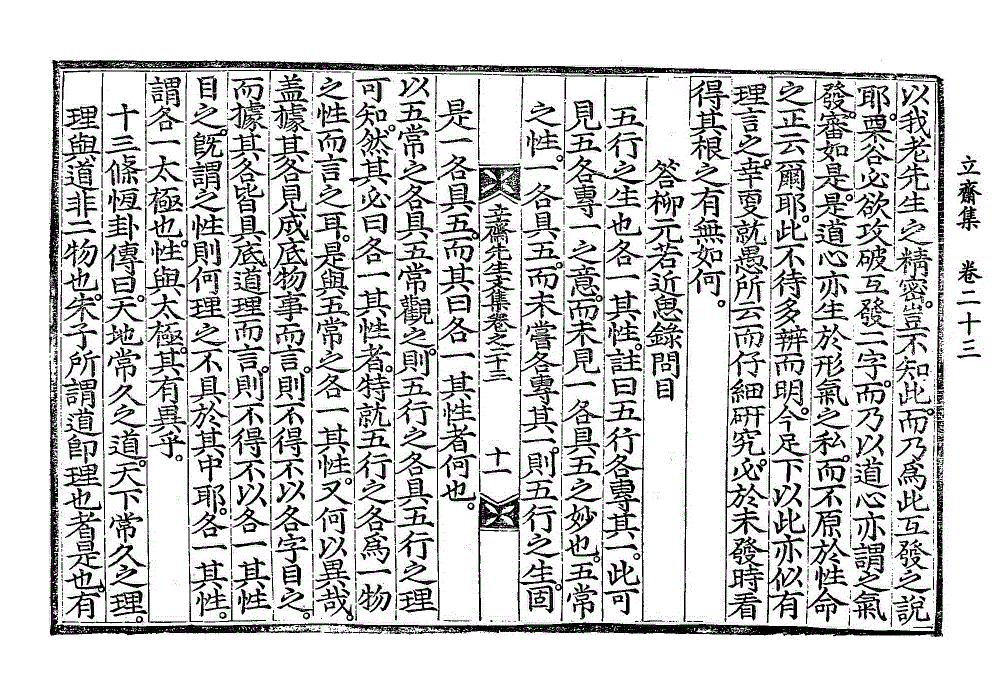 以我老先生之精密。岂不知此。而乃为此互发之说耶。栗谷必欲攻破互发二字。而乃以道心亦谓之气发。审如是。是道心亦生于形气之私。而不原于性命之正云尔耶。此不待多辨而明。今足下以此亦似有理言之。幸更就愚所云而仔细研究。必于未发时看得其根之有无如何。
以我老先生之精密。岂不知此。而乃为此互发之说耶。栗谷必欲攻破互发二字。而乃以道心亦谓之气发。审如是。是道心亦生于形气之私。而不原于性命之正云尔耶。此不待多辨而明。今足下以此亦似有理言之。幸更就愚所云而仔细研究。必于未发时看得其根之有无如何。答柳元若近思录问目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注曰五行各专其一。此可见五各专一之意。而未见一各具五之妙也。五常之性。一各具五。而未尝各专其一。则五行之生。固是一各具五。而其曰各一其性者何也。
以五常之各具五常观之。则五行之各具五行之理可知。然其必曰各一其性者。特就五行之各为一物之性而言之耳。是与五常之各一其性。又何以异哉。盖据其各见成底物事而言。则不得不以各字目之。而据其各皆具底道理而言。则不得不以各一其性目之。既谓之性则何理之不具于其中耶。各一其性。谓各一太极也。性与太极。其有异乎。
十三条恒卦传曰。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理与道非二物也。朱子所谓道即理也者是也。有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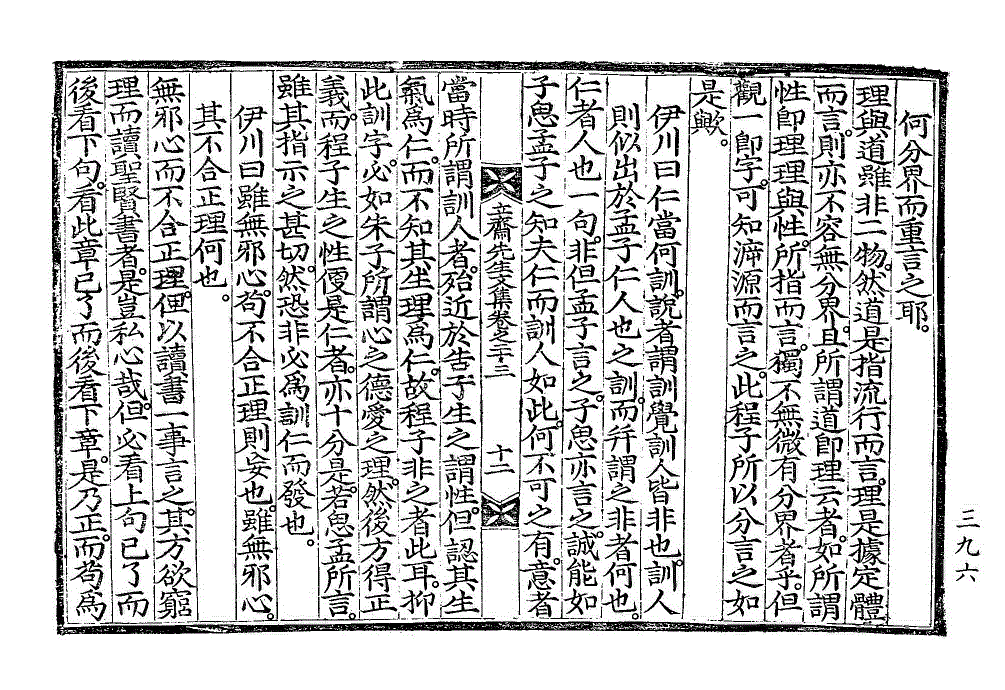 何分界而重言之耶。
何分界而重言之耶。理与道虽非二物。然道是指流行而言。理是据定体而言。则亦不容无分界。且所谓道即理云者。如所谓性即理理与性。所指而言。独不无微有分界者乎。但观一即字。可知溯源而言之。此程子所以分言之如是欤。
伊川曰仁当何训。说者谓训觉训人皆非也。训人则似出于孟子仁人也之训。而并谓之非者何也。
仁者人也一句。非但孟子言之。子思亦言之。诚能如子思孟子之知夫仁而训人如此。何不可之有。意者当时所谓训人者。殆近于告子生之谓性。但认其生气为仁。而不知其生理为仁。故程子非之者此耳。抑此训字。必如朱子所谓心之德爱之理。然后方得正义。而程子生之性便是仁者。亦十分是。若思孟所言。虽其指示之甚切。然恐非必为训仁而发也。
伊川曰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虽无邪心。其不合正理何也。
无邪心而不合正理。但以读书一事言之。其方欲穷理而读圣贤书者。是岂私心哉。但必看上句已了而后看下句。看此章已了而后看下章。是乃正。而苟为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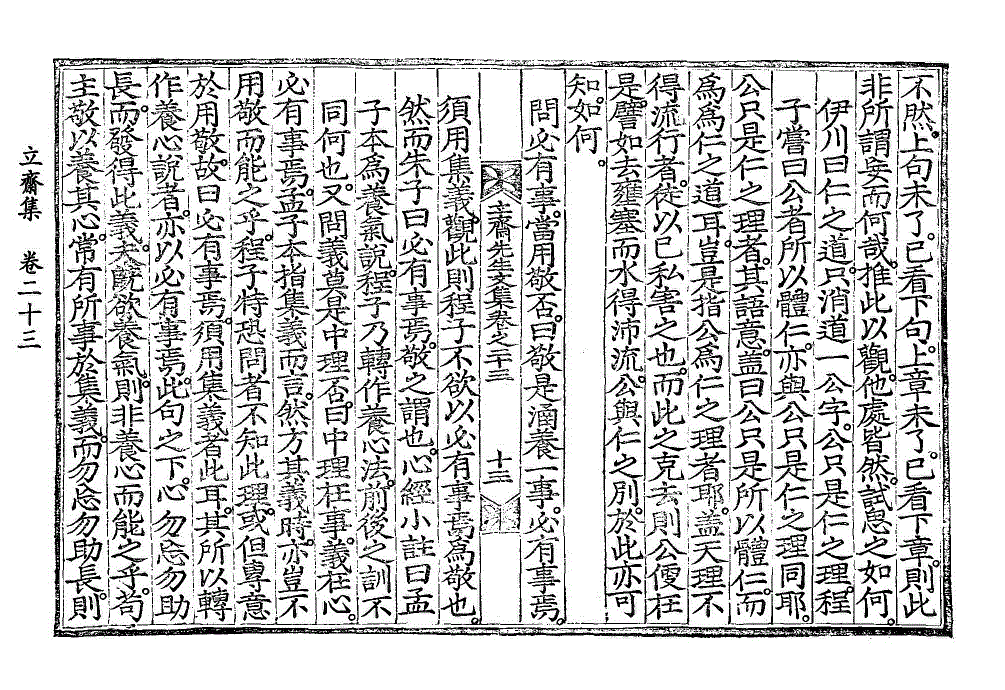 不然。上句未了。已看下句。上章未了。已看下章。则此非所谓妄而何哉。推此以观。他处皆然。试思之如何。
不然。上句未了。已看下句。上章未了。已看下章。则此非所谓妄而何哉。推此以观。他处皆然。试思之如何。伊川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程子尝曰公者所以体仁。亦与公只是仁之理同耶。
公只是仁之理者。其语意。盖曰公只是所以体仁。而为为仁之道耳。岂是指公为仁之理者耶。盖天理不得流行者。徒以己私害之也。而此之克去则公便在是。譬如去壅塞而水得沛流。公与仁之别。于此亦可知。如何。
问必有事。当用敬否。曰敬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用集义。观此则程子不欲以必有事焉为敬也。然而朱子曰必有事焉。敬之谓也。心经小注曰孟子本为养气说。程子乃转作养心法。前后之训不同何也。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
必有事焉。孟子本指集义而言。然方其义时。亦岂不用敬而能之乎。程子特恐问者不知此理。或但专意于用敬。故曰必有事焉。须用集义者此耳。其所以转作养心说者。亦以必有事焉。此句之下。心勿忘勿助长。而发得此义。夫既欲养气。则非养心而能之乎。苟主敬以养其心。常有所事于集义。而勿忘勿助长。则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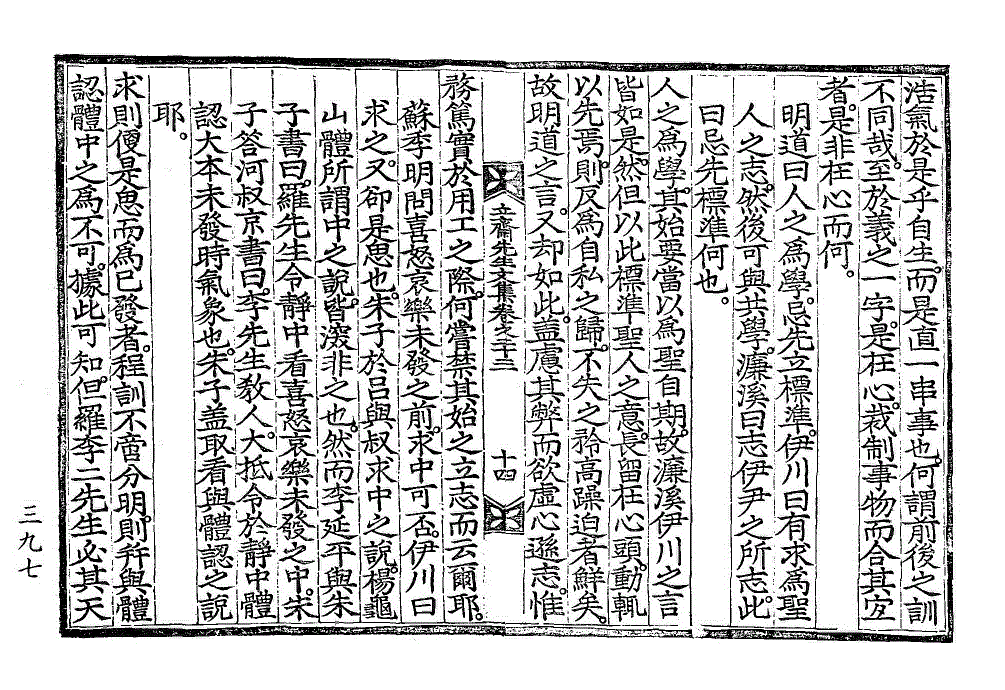 浩气于是乎自生。而是直一串事也。何谓前后之训不同哉。至于义之一字。是在心。裁制事物而合其宜者。是非在心而何。
浩气于是乎自生。而是直一串事也。何谓前后之训不同哉。至于义之一字。是在心。裁制事物而合其宜者。是非在心而何。明道曰人之为学。忌先立标准。伊川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此曰忌先标准何也。
人之为学。其始要当以为圣自期。故濂溪伊川之言皆如是。然但以此标准圣人之意。长留在心头。动辄以先焉。则反为自私之归。不失之矜高躁迫者鲜矣。故明道之言。又却如此。盖虑其弊而欲虚心逊志。惟务笃实于用工之际。何尝禁其始之立志而云尔耶。
苏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求之。又却是思也。朱子于吕与叔求中之说。杨龟山体所谓中之说。皆深非之也。然而李延平与朱子书曰。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朱子答河叔京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也。朱子盖取看与体认之说耶。
求则便是思而为已发者。程训不啻分明。则并与体认体中之为不可。据此可知。但罗李二先生必其天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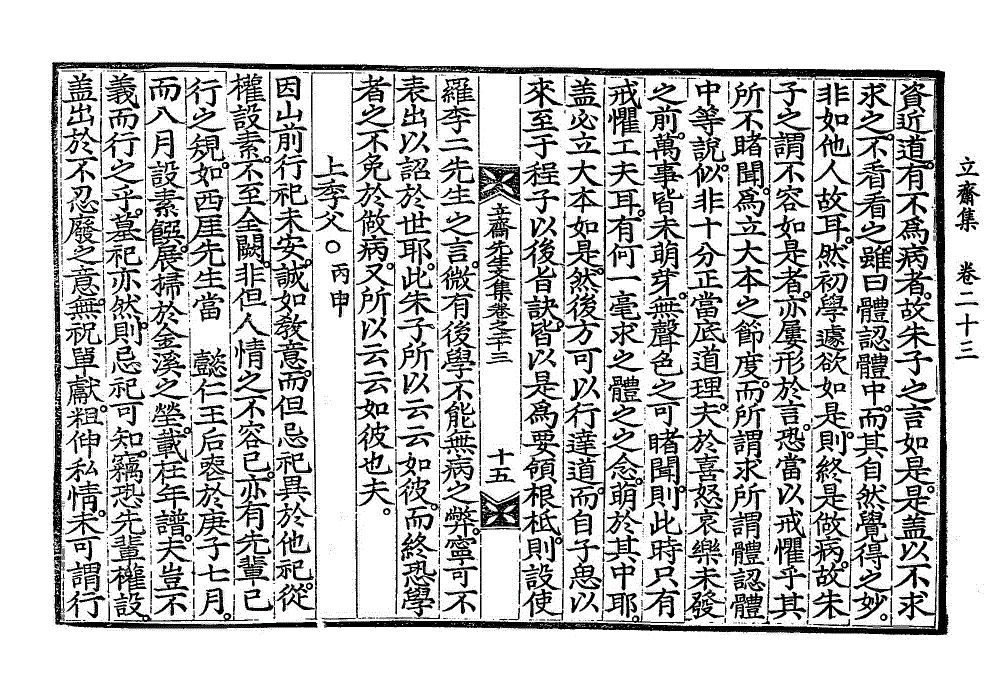 资近道。有不为病者。故朱子之言如是。是盖以不求求之。不看看之。虽曰体认体中。而其自然觉得之妙。非如他人故耳。然初学遽欲如是。则终是做病。故朱子之谓不容如是者。亦屡形于言。恐当以戒惧乎其所不睹闻。为立大本之节度。而所谓求所谓体认体中等说。似非十分正当底道理。夫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万事皆未萌芽。无声色之可睹闻。则此时只有戒惧工夫耳。有何一毫求之体之之念。萌于其中耶。盖必立大本如是。然后方可以行达道。而自子思以来至于程子以后旨诀。皆以是为要领根柢。则设使罗李二先生之言。微有后学不能无病之弊。宁可不表出以诏于世耶。此朱子所以云云如彼。而终恐学者之不免于做病。又所以云云如彼也夫。
资近道。有不为病者。故朱子之言如是。是盖以不求求之。不看看之。虽曰体认体中。而其自然觉得之妙。非如他人故耳。然初学遽欲如是。则终是做病。故朱子之谓不容如是者。亦屡形于言。恐当以戒惧乎其所不睹闻。为立大本之节度。而所谓求所谓体认体中等说。似非十分正当底道理。夫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万事皆未萌芽。无声色之可睹闻。则此时只有戒惧工夫耳。有何一毫求之体之之念。萌于其中耶。盖必立大本如是。然后方可以行达道。而自子思以来至于程子以后旨诀。皆以是为要领根柢。则设使罗李二先生之言。微有后学不能无病之弊。宁可不表出以诏于世耶。此朱子所以云云如彼。而终恐学者之不免于做病。又所以云云如彼也夫。上季父(丙申)
因山前行祀未安。诚如教意。而但忌祀异于他祀。从权设素。不至全阙。非但人情之不容已。亦有先辈已行之规。如西厓先生当 懿仁王后丧于庚子七月。而八月设素馔。展扫于金溪之茔。载在年谱。夫岂不义而行之乎。墓祀亦然。则忌祀可知。窃恐先辈权设。盖出于不忍废之意。无祝单献。粗伸私情。未可谓行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8L 页
 祭。则亦何妨于遵 朝令耶。略送官需。恐不至大未安。如何如何。
祭。则亦何妨于遵 朝令耶。略送官需。恐不至大未安。如何如何。与从君时晦别纸
渔轩赵哀家变礼。今见杜陵别纸。则所论与吾无异同。其曰接其祖未尽之服。而与叠承重义例差别者。诚为得之。至于神主之不改题。祝文之书以丧人代数。又是不得已者。卒哭后以练布受服似当。至于恒着则承重斩衰。重于续服齐衰。而比诸练服尤重。当以斩衰为恒着之服。惟在曾祖母殡中用练服可也。其三殡告辞。考之退陶集中。亦有明据。于曾祖妣殡则小祥前夕。当曰伏以丧未及练。祖考又殁。向值祥日。祭以是阙。今经襄奉。卜日将事。未尽之服。小子是嗣。叠哀又加。五内如磔。敢趁前夕。告此罔极。于祖殡则曾祖妣小祥前夕。亦当曰伏以小子不天。祸又至斯。上殡下殡。主丧更谁。续服尸祭。咸丁微躯。情礼莫比。叫苦陈由。于父殡则当位小祥前夕。亦当曰伏以祖考在时。主府君丧。神主称号。到今非当。三年之内。无改题礼。然惟祝式。宜称考祭。仰瞻俯读。此何变节。哭告厥由。穹壤痛彻云云。此意及于彼中如何。
寄儿象晋(己酉)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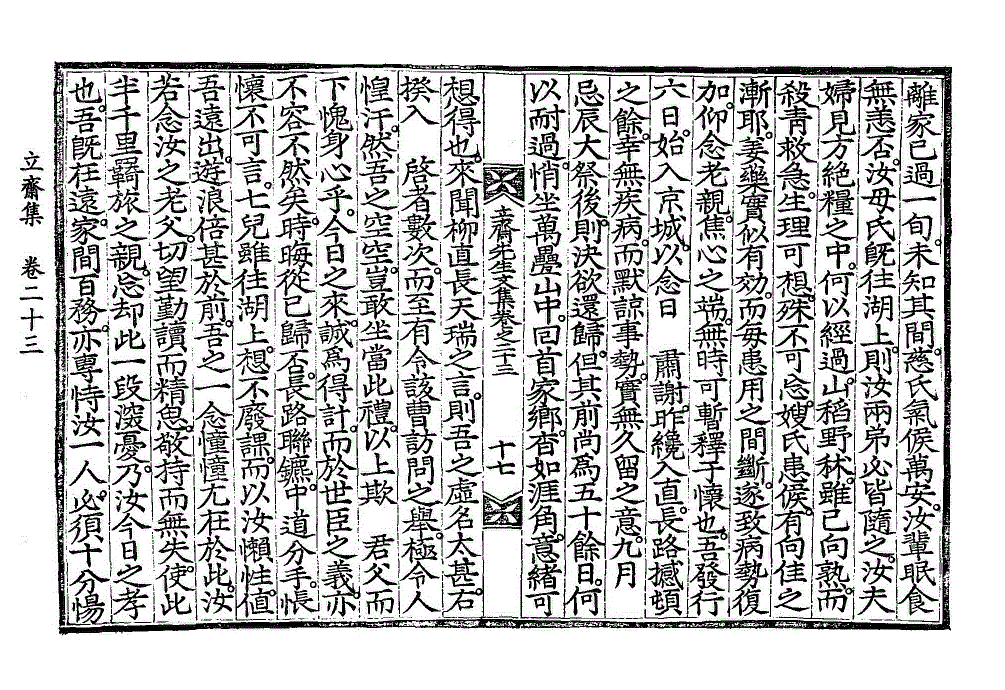 离家已过一旬。未知其间。慈氏气候万安。汝辈眠食无恙否。汝母氏既往湖上。则汝两弟必皆随之。汝夫妇见方绝粮之中。何以经过。山稻野秫。虽已向熟。而杀青救急。生理可想。殊不可忘。嫂氏患候。有向佳之渐耶。姜药实似有效。而每患用之间断。遂致病势复加。仰念老亲。焦心之端。无时可暂释于怀也。吾发行六日。始入京城。以念日 肃谢。昨才入直。长路撼顿之馀。幸无疾病。而默谅事势。实无久留之意。九月 忌辰大祭后。则决欲还归。但其前尚为五十馀日。何以耐过。悄坐万叠山中。回首家乡。杳如涯角。意绪可想得也。来闻柳直长天瑞之言。则吾之虚名太甚。右揆入 启者数次。而至有令该曹访问之举。极令人惶汗。然吾之空空。岂敢坐当此礼。以上欺 君父而下愧身心乎。今日之来。诚为得计。而于世臣之义。亦不容不然矣。时晦从已归否。长路联镳。中道分手。怅怀不可言。七儿虽往湖上。想不废课。而以汝懒性。值吾远出。游浪倍甚于前。吾之一念憧憧尤在于此。汝若念汝之老父。切望勤读而精思。敬持而无失。使此半千里羁旅之亲。忘却此一段深忧。乃汝今日之孝也。吾既在远。家间百务。亦专恃汝一人。必须十分惕
离家已过一旬。未知其间。慈氏气候万安。汝辈眠食无恙否。汝母氏既往湖上。则汝两弟必皆随之。汝夫妇见方绝粮之中。何以经过。山稻野秫。虽已向熟。而杀青救急。生理可想。殊不可忘。嫂氏患候。有向佳之渐耶。姜药实似有效。而每患用之间断。遂致病势复加。仰念老亲。焦心之端。无时可暂释于怀也。吾发行六日。始入京城。以念日 肃谢。昨才入直。长路撼顿之馀。幸无疾病。而默谅事势。实无久留之意。九月 忌辰大祭后。则决欲还归。但其前尚为五十馀日。何以耐过。悄坐万叠山中。回首家乡。杳如涯角。意绪可想得也。来闻柳直长天瑞之言。则吾之虚名太甚。右揆入 启者数次。而至有令该曹访问之举。极令人惶汗。然吾之空空。岂敢坐当此礼。以上欺 君父而下愧身心乎。今日之来。诚为得计。而于世臣之义。亦不容不然矣。时晦从已归否。长路联镳。中道分手。怅怀不可言。七儿虽往湖上。想不废课。而以汝懒性。值吾远出。游浪倍甚于前。吾之一念憧憧尤在于此。汝若念汝之老父。切望勤读而精思。敬持而无失。使此半千里羁旅之亲。忘却此一段深忧。乃汝今日之孝也。吾既在远。家间百务。亦专恃汝一人。必须十分惕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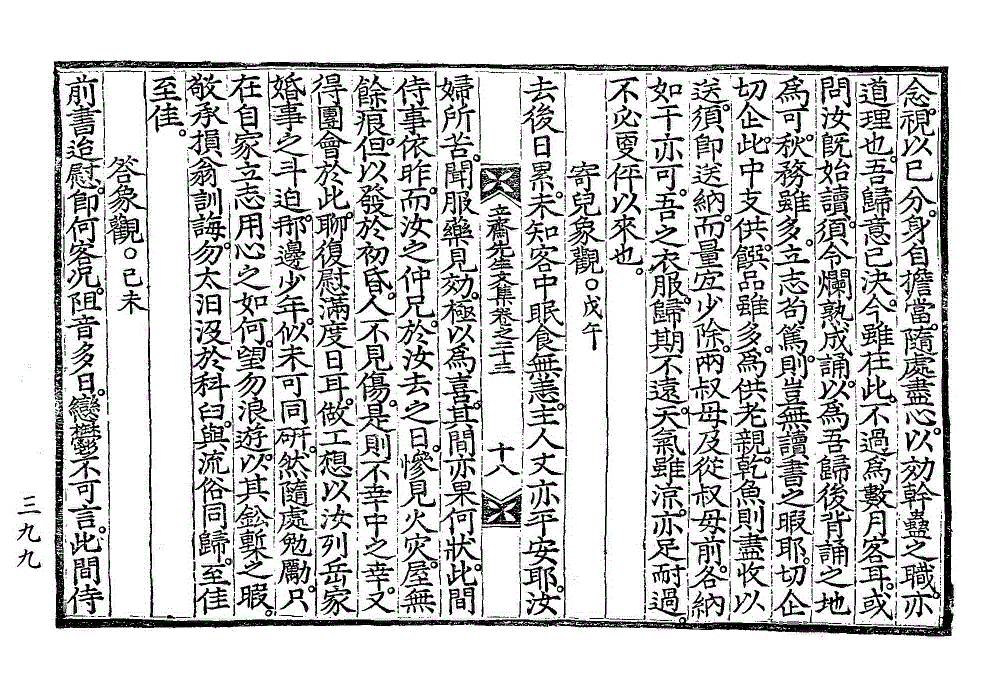 念。视以己分。身自担当。随处尽心。以效干蛊之职。亦道理也。吾归意已决。今虽在此。不过为数月客耳。或问汝既始读。须令烂熟成诵。以为吾归后背诵之地为可。秋务虽多。立志苟笃。则岂无读书之暇耶。切企切企。此中支供。馔品虽多。为供老亲。乾鱼则尽收以送。须即送纳。而量宜少除。两叔母及从叔母前。各纳如干亦可。吾之衣服。归期不远。天气虽凉。亦足耐过。不必更伻以来也。
念。视以己分。身自担当。随处尽心。以效干蛊之职。亦道理也。吾归意已决。今虽在此。不过为数月客耳。或问汝既始读。须令烂熟成诵。以为吾归后背诵之地为可。秋务虽多。立志苟笃。则岂无读书之暇耶。切企切企。此中支供。馔品虽多。为供老亲。乾鱼则尽收以送。须即送纳。而量宜少除。两叔母及从叔母前。各纳如干亦可。吾之衣服。归期不远。天气虽凉。亦足耐过。不必更伻以来也。寄儿象观(戊午)
去后日累。未知客中眠食无恙。主人丈亦平安耶。汝妇所苦。闻服药见效。极以为喜。其间亦果何状。此间侍事依昨。而汝之仲兄。于汝去之日。惨见火灾。屋无馀痕。但以发于初昏。人不见伤。是则不幸中之幸。又得团会于此。聊复慰满度日耳。做工想以汝列岳家婚事之斗迫。那边少年。似未可同研。然随处勉励。只在自家立志用心之如何。望勿浪游。以其铅椠之暇。敬承损翁训诲。勿太汩没于科臼。与流俗同归。至佳至佳。
答象观(己未)
前书迨慰。即何客况。阻音多日。恋郁不可言。此间侍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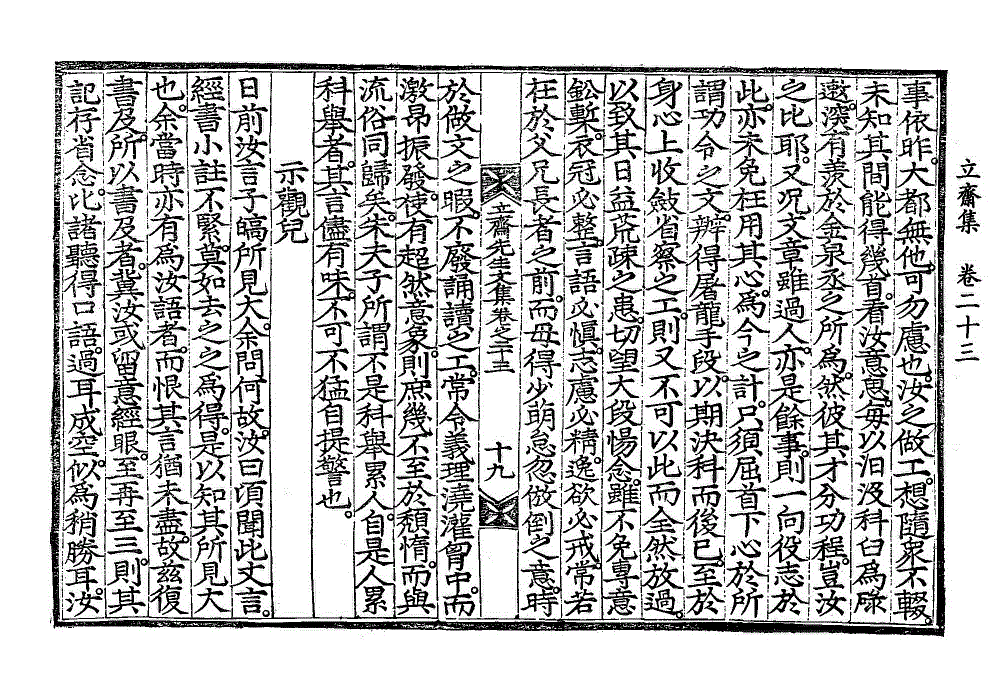 事依昨。大都无他。可勿虑也。汝之做工。想随众不辍。未知其间能得几首。看汝意思。每以汩没科臼为碌遫。深有羡于金泉丞之所为。然彼其才分功程。岂汝之比耶。又况文章虽过人。亦是馀事。则一向役志于此。亦未免枉用其心。为今之计。只须屈首下心于所谓功令之文。办得屠龙手段。以期决科而后已。至于身心上收敛省察之工。则又不可以此而全然放过。以致其日益荒疏之患。切望大段惕念。虽不免专意铅椠。衣冠必整。言语必慎。志虑必精。逸欲必戒。常若在于父兄长者之前。而毋得少萌怠忽仿倒之意。时于做文之暇。不废诵读之工。常令义理浇灌胸中。而激昂振发。使有超然意象。则庶几不至于颓惰。而与流俗同归矣。朱夫子所谓不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者。其言尽有味。不可不猛自提警也。
事依昨。大都无他。可勿虑也。汝之做工。想随众不辍。未知其间能得几首。看汝意思。每以汩没科臼为碌遫。深有羡于金泉丞之所为。然彼其才分功程。岂汝之比耶。又况文章虽过人。亦是馀事。则一向役志于此。亦未免枉用其心。为今之计。只须屈首下心于所谓功令之文。办得屠龙手段。以期决科而后已。至于身心上收敛省察之工。则又不可以此而全然放过。以致其日益荒疏之患。切望大段惕念。虽不免专意铅椠。衣冠必整。言语必慎。志虑必精。逸欲必戒。常若在于父兄长者之前。而毋得少萌怠忽仿倒之意。时于做文之暇。不废诵读之工。常令义理浇灌胸中。而激昂振发。使有超然意象。则庶几不至于颓惰。而与流俗同归矣。朱夫子所谓不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者。其言尽有味。不可不猛自提警也。示观儿
日前汝言子皓所见大。余问何故。汝曰顷闻此丈言。经书小注不紧。莫如去之之为得。是以知其所见大也。余当时亦有为汝语者。而恨其言犹未尽。故玆复书及。所以书及者。冀汝或留意经眼。至再至三。则其记存省念。比诸听得口语。过耳成空。似为稍胜耳。汝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0L 页
 能知此意否。大抵汝之病痛。在于心粗气粗。从来不能吃辛耐烦。故凡古人文字。极其细密。政好玩索处。一皆厌看而厌思之。遂从吾性质偏处。别生见解。即谓圣经贤传。只得通其大义则斯已足矣。乌用是辨论为哉。于是焉又自断决。作为一副定本。虽父兄所为。亦不满于心。况他人乎。想子皓必不知汝意如此。又渠穷格之工。过人远甚。诚见先儒之说间不免有疏漏支蔓处。而虽其极分晓不可无者。其心以为太泄露无馀蕴。使学者不得自去理会。而厥或径先看此。则反滋其惑。有如谷腾雾波滚沙之为。故其言如是耳。汝乃不知其然。深喜其言之合于汝意。是亦粗粗之一端也。彼时吾为汝语。但云古人用尽精力看出经书旨意。说出多少议论者。本欲其有益于后人而为是焉。则不可忽明矣。又幸得入于小注。使千万世之下。皆知某某之羽翼圣经者。非但于自家亦为附骥之荣。而自永乐以后至今印行于世。已成铁定完本。则其不可去又明矣。汝若厌看则汝独不看可矣。何轻易信此言也。如汝之见。虽朱子所注。亦必以为不紧。此非细忧云云。而看汝气色。似藐藐然听之。今虽书及如此。又安望其果能记存而省念之耶。只
能知此意否。大抵汝之病痛。在于心粗气粗。从来不能吃辛耐烦。故凡古人文字。极其细密。政好玩索处。一皆厌看而厌思之。遂从吾性质偏处。别生见解。即谓圣经贤传。只得通其大义则斯已足矣。乌用是辨论为哉。于是焉又自断决。作为一副定本。虽父兄所为。亦不满于心。况他人乎。想子皓必不知汝意如此。又渠穷格之工。过人远甚。诚见先儒之说间不免有疏漏支蔓处。而虽其极分晓不可无者。其心以为太泄露无馀蕴。使学者不得自去理会。而厥或径先看此。则反滋其惑。有如谷腾雾波滚沙之为。故其言如是耳。汝乃不知其然。深喜其言之合于汝意。是亦粗粗之一端也。彼时吾为汝语。但云古人用尽精力看出经书旨意。说出多少议论者。本欲其有益于后人而为是焉。则不可忽明矣。又幸得入于小注。使千万世之下。皆知某某之羽翼圣经者。非但于自家亦为附骥之荣。而自永乐以后至今印行于世。已成铁定完本。则其不可去又明矣。汝若厌看则汝独不看可矣。何轻易信此言也。如汝之见。虽朱子所注。亦必以为不紧。此非细忧云云。而看汝气色。似藐藐然听之。今虽书及如此。又安望其果能记存而省念之耶。只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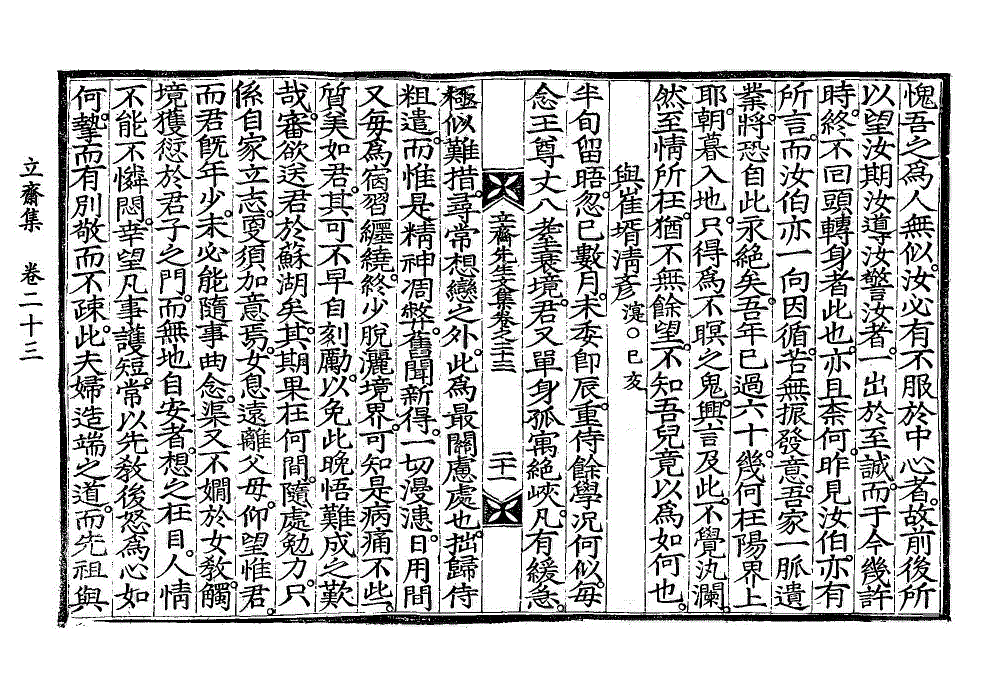 愧吾之为人无似。汝必有不服于中心者。故前后所以望汝期汝导汝警汝者。一出于至诚。而于今几许时。终不回头转身者此也。亦且柰何。昨见汝伯。亦有所言。而汝伯亦一向因循。苦无振发意。吾家一脉遗业。将恐自此永绝矣。吾年已过六十。几何在阳界上耶。朝暮入地。只得为不瞑之鬼。兴言及此。不觉汍澜。然至情所在。犹不无馀望。不知吾儿竟以为如何也。
愧吾之为人无似。汝必有不服于中心者。故前后所以望汝期汝导汝警汝者。一出于至诚。而于今几许时。终不回头转身者此也。亦且柰何。昨见汝伯。亦有所言。而汝伯亦一向因循。苦无振发意。吾家一脉遗业。将恐自此永绝矣。吾年已过六十。几何在阳界上耶。朝暮入地。只得为不瞑之鬼。兴言及此。不觉汍澜。然至情所在。犹不无馀望。不知吾儿竟以为如何也。与崔婿清彦(湜○己亥)
半旬留晤。忽已数月。未委即辰。重侍馀学况何似。每念王尊丈八耋衰境。君又单身孤寓绝峡。凡有缓急。极似难措。寻常想恋之外。此为最关虑处也。拙归侍粗遣。而惟是精神凋弊。旧闻新得。一切漫漶。日用间又每为宿习缠绕。终少脱洒境界。可知是病痛不些。质美如君。其可不早自刻励。以免此晚悟难成之叹哉。审欲送君于苏湖矣。其期果在何间。随处勉力。只系自家立志。更须加意焉。女息远离父母。仰望惟君。而君既年少。未必能随事曲念。渠又不娴于女教。触境获愆于君子之门。而无地自安者。想之在目。人情不能不怜闷。幸望凡事护短。常以先教后怒为心如何。挚而有别敬而不疏。此夫妇造端之道。而先祖与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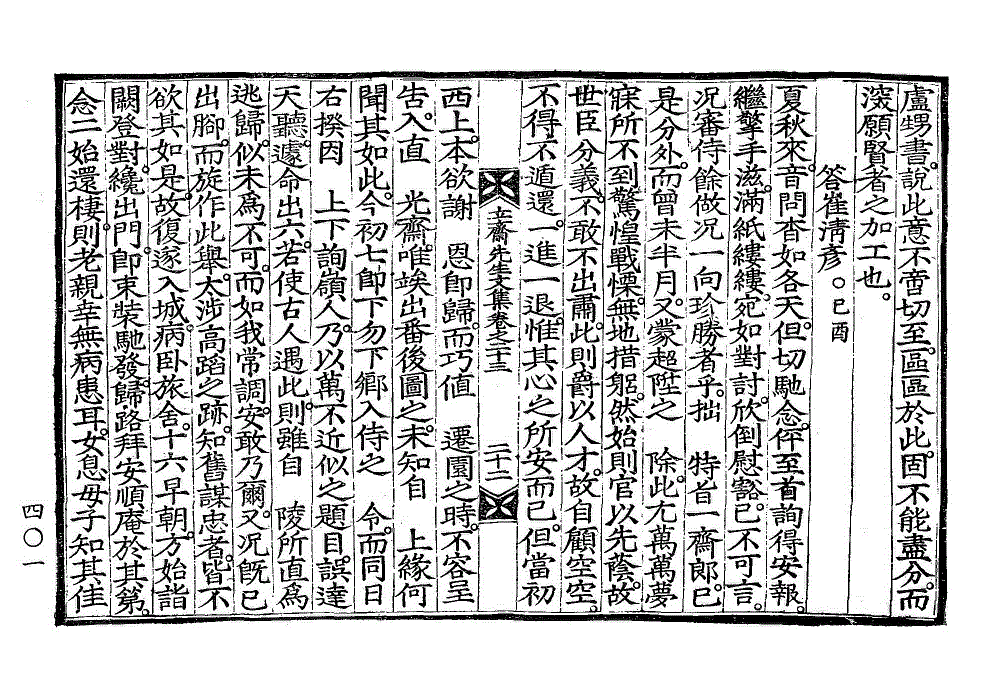 卢甥书。说此意不啻切至。区区于此。固不能尽分。而深愿贤者之加工也。
卢甥书。说此意不啻切至。区区于此。固不能尽分。而深愿贤者之加工也。答崔清彦(己酉)
夏秋来。音问杳如各天。但切驰念。伻至首询得安报。继擎手滋。满纸缕缕。宛如对讨。欣倒慰豁。已不可言。况审侍馀做况一向珍胜者乎。拙 特旨一斋郎。已是分外。而曾未半月。又蒙超升之 除。此尤万万梦寐所不到。惊惶战慄。无地措躬。然始则官以先荫。故世臣分义。不敢不出肃。此则爵以人才。故自顾空空。不得不遁还。一进一退。惟其心之所安而已。但当初西上。本欲谢 恩即归。而巧值 迁园之时。不容呈告。入直 光斋。唯俟出番后图之。未知自 上缘何闻其如此。今初七即下勿下乡入侍之 令。而同日右揆因 上下询岭人。乃以万不近似之题目。误达天听。遽命出六。若使古人遇此。则虽自 陵所直为逃归。似未为不可。而如我常调。安敢乃尔。又况既已出脚。而旋作此举。太涉高蹈之迹。知旧谋忠者。皆不欲其如是。故复遂入城。病卧旅舍。十六早朝。方始诣阙登对。才出门。即束装驰发。归路拜安顺庵于其第。念二始还栖。则老亲幸无病患耳。女息母子知其佳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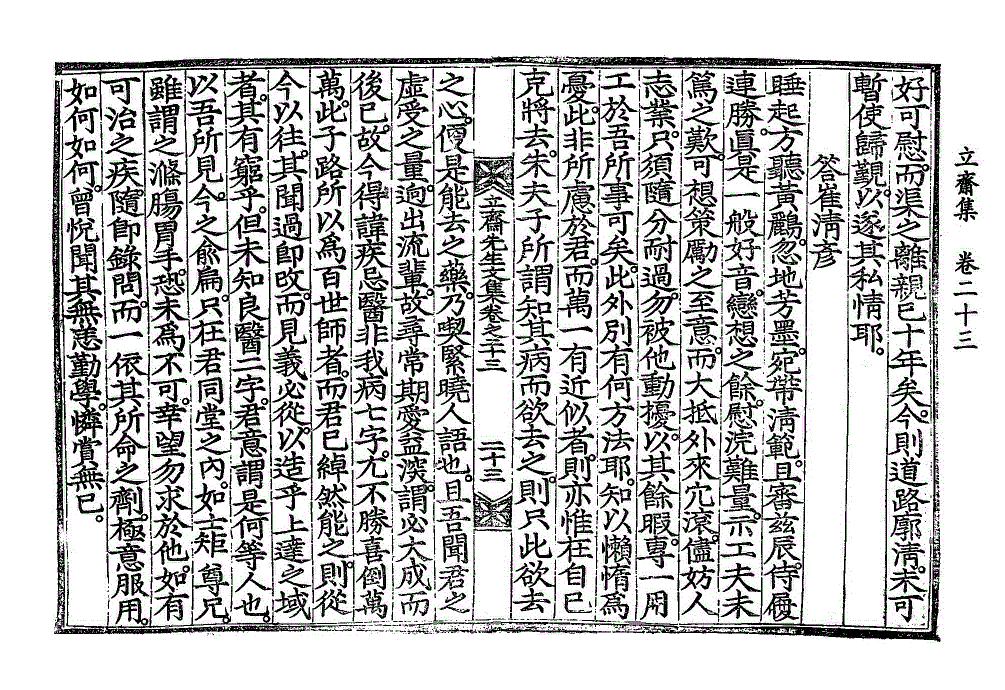 好可慰。而渠之离亲已十年矣。今则道路廓清。未可暂使归觐。以遂其私情耶。
好可慰。而渠之离亲已十年矣。今则道路廓清。未可暂使归觐。以遂其私情耶。答崔清彦
睡起方听黄鹂。忽地芳墨。宛带清范。且审玆辰。侍履连胜。真是一般好音。恋想之馀。慰浣难量。示工夫未笃之叹。可想策励之至意。而大抵外来冗滚。尽妨人志业。只须随分耐过。勿被他动扰。以其馀暇。专一用工于吾所事可矣。此外别有何方法耶。知以懒惰为忧。此非所虑于君。而万一有近似者。则亦惟在自己克将去。朱夫子所谓知其病而欲去之。则只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药。乃吃紧晓人语也。且吾闻君之虚受之量。迥出流辈。故寻常期爱益深。谓必大成而后已。故今得讳疾忌医非我病七字。尤不胜喜倒万万。此子路所以为百世师者。而君已绰然能之。则从今以往。其闻过即改。而见义必从。以造乎上达之域者。其有穷乎。但未知良医二字。君意谓是何等人也。以吾所见。今之俞扁。只在君同堂之内。如士矩尊兄。虽谓之涤肠胃手。恐未为不可。幸望勿求于他。如有可治之疾。随即录问。而一依其所命之剂。极意服用。如何如何。曾悦闻其无恙勤学。怜赏无已。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2L 页
 与崔清彦(甲寅)
与崔清彦(甲寅)匪意获奉堂叔。欣倒之馀。叩闻侍学连胜。慰豁无已。每念君英气过人。寻常识度。尽有伟然处。而至于静密意思。终似不足。故前此亦尝以此奉规矣。未知能不以为非。而肯垂采听否耶。今日治心下工之法。莫过于圣贤书。而若其最切要者。则又无出于四子朱文之外。想君已所读过。然幸望就此而益加温理之工。字研句索。期于融贯而后已。则将见心地自然定贴。自然虚明。其于天下之理。见得必详。而发于云为之间者。亦当自至于从容曲尽之境。无复粗疏之患矣。千万细思而深量之。试下手以观如何。
答赵甥彦儒彦休(辛酉)
伯也之占解旋屈。仲也之期逝不来。俱令人怅失不寻常。此际君大人忽临。各经草土之馀。悲喜交并。因获佥手滋。知侍学连胜。慰不可言。吾近以感气吟苦。但自孙妇入门后。浑室慰满度了。此外无足烦远书也。君辈知能留意于实工夫。好消息孰过于是。勉之勉之。为士者志业。不惟在决科第一事。想所闻于师门者亦然。果能卓然立志。随事省察。以得其真味。自当欲住而不能矣。勿以未来此中为恨。益加勉励。无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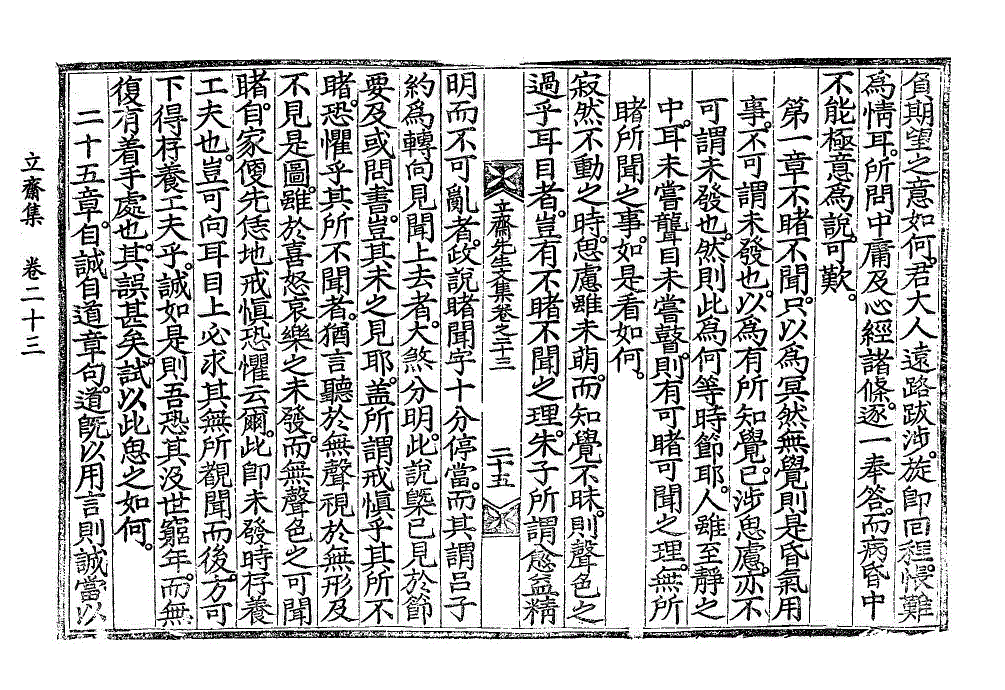 负期望之意如何。君大人远路跋涉。旋即回程。怅难为情耳。所问中庸及心经诸条。逐一奉答。而病昏中不能极意为说。可叹。
负期望之意如何。君大人远路跋涉。旋即回程。怅难为情耳。所问中庸及心经诸条。逐一奉答。而病昏中不能极意为说。可叹。第一章不睹不闻。只以为冥然无觉则是昏气用事。不可谓未发也。以为有所知觉。已涉思虑。亦不可谓未发也。然则此为何等时节耶。人虽至静之中。耳未尝聋目未尝瞽。则有可睹可闻之理。无所睹所闻之事。如是看如何。
寂然不动之时。思虑虽未萌。而知觉不昧。则声色之过乎耳目者。岂有不睹不闻之理。朱子所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者。政说睹闻字十分停当。而其谓吕子约为转向见闻上去者。大煞分明。此说槩已见于节要及或问书。岂其未之见耶。盖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者。犹言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及不见是图。虽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而无声色之可闻睹。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惧云尔。此即未发时存养工夫也。岂可向耳目上必求其无所睹闻而后。方可下得存养工夫乎。诚如是则吾恐其没世穷年。而无复有着手处也。其误甚矣。试以此思之如何。
二十五章。自诚自道章句。道既以用言则诚当以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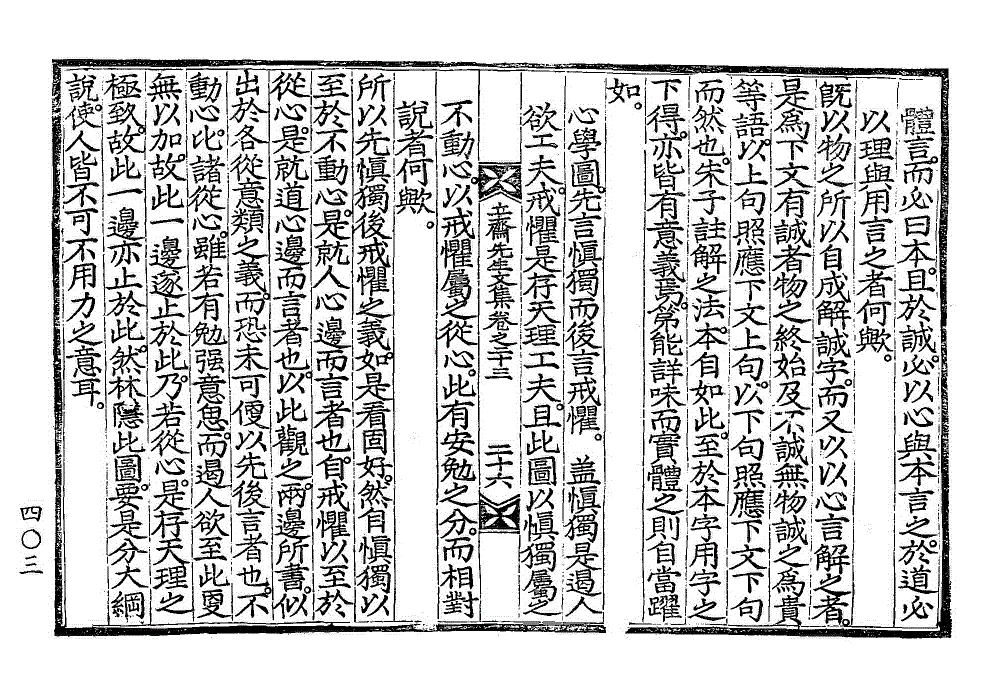 体言。而必曰本。且于诚。必以心与本言之。于道必以理与用言之者何欤。
体言。而必曰本。且于诚。必以心与本言之。于道必以理与用言之者何欤。既以物之所以自成解诚字。而又以以心言解之者。是为下文有诚者物之终始及不诚无物诚之为贵等语。以上句照应下文上句。以下句照应下文下句而然也。朱子注解之法。本自如此。至于本字用字之下得。亦皆有意义焉。第能详味而实体之则自当跃如。
心学图。先言慎独而后言戒惧。 盖慎独是遏人欲工夫。戒惧是存天理工夫。且此图以慎独属之不动心。以戒惧属之从心。此有安勉之分。而相对说者何欤。
所以先慎独后戒惧之义。如是看固好。然自慎独以至于不动心。是就人心边而言者也。自戒惧以至于从心。是就道心边而言者也。以此观之。两边所书。似出于各从意类之义。而恐未可便以先后言者也。不动心。比诸从心。虽若有勉强意思。而遏人欲至此更无以加。故此一边遂止于此。乃若从心。是存天理之极致。故此一边亦止于此。然林隐此图。要是分大纲说。使人皆不可不用力之意耳。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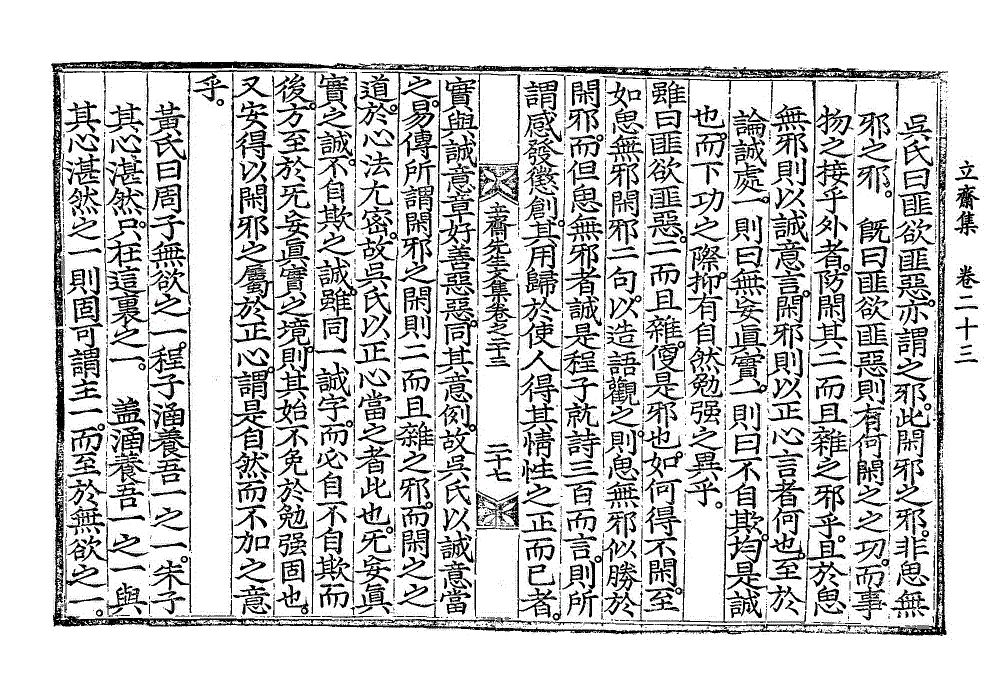 吴氏曰匪欲匪恶。亦谓之邪。此闲邪之邪。非思无邪之邪。 既曰匪欲匪恶则有何闲之之功。而事物之接乎外者。防闲其二而且杂之邪乎。且于思无邪则以诚意言。闲邪则以正心言者何也。至于论诚处。一则曰无妄真实。一则曰不自欺。均是诚也。而下功之际。抑有自然勉强之异乎。
吴氏曰匪欲匪恶。亦谓之邪。此闲邪之邪。非思无邪之邪。 既曰匪欲匪恶则有何闲之之功。而事物之接乎外者。防闲其二而且杂之邪乎。且于思无邪则以诚意言。闲邪则以正心言者何也。至于论诚处。一则曰无妄真实。一则曰不自欺。均是诚也。而下功之际。抑有自然勉强之异乎。虽曰匪欲匪恶。二而且杂。便是邪也。如何得不闲。至如思无邪闲邪二句。以造语观之。则思无邪似胜于闲邪。而但思无邪者诚是程子就诗三百而言。则所谓感发惩创。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者。实与诚意章好善恶恶。同其意例。故吴氏以诚意当之。易传所谓闲邪之闲则二而且杂之邪。而闲之之道。于心法尤密。故吴氏以正心当之者此也。无妄真实之诚。不自欺之诚。虽同一诚字。而必自不自欺而后。方至于无妄真实之境。则其始不免于勉强固也。又安得以闲邪之属于正心。谓是自然而不加之意乎。
黄氏曰周子无欲之一。程子涵养吾一之一。朱子其心湛然。只在这里之一。 盖涵养吾一之一与其心湛然之一则固可谓主一。而至于无欲之一。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4L 页
 似不可谓主一矣。同谓之主一者何也。
似不可谓主一矣。同谓之主一者何也。一者无欲。朱子谓这话头高。猝急难凑泊。此盖指工夫极处而言者。然苟非其始之主于一。接续无间断。则何以得成功如是乎。无欲之一。专在于主一之工。故并此而一例言之。且不论用工与成功。就一字而观之则当此之时。非所谓太极之境界而何。此段立论主意。正在此一句上。只如是认取恐宜耳。
真氏曰绝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则礼复矣。故曰无己可克。 绝四与能敬。有克己无克之不同。则敬工夫尤切于绝四之道耶。
看得是。
朱子言谨独处。或曰不止念虑初萌。只自知处。或曰是就中有一念萌动处。尤当致谨。 二说不同何耶。
不论念虑之初萌已萌。其为自知则审矣。慎独之工。尤在于此处。今但依此训做去而已。有何二说不同之疑耶。
朱子曰大人心下。没许多事。 大人之心。通达万变。则何以谓之没许多事耶。
大人之心。虽通达万变。而所谓万变者。只是心所具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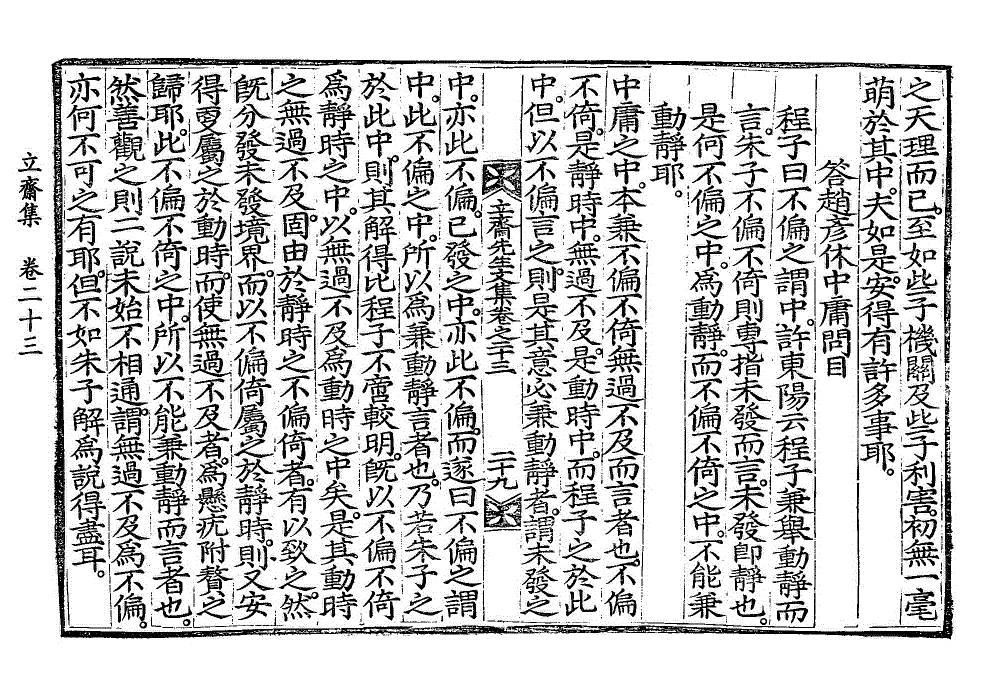 之天理而已。至如些子机关及些子利害。初无一毫萌于其中。夫如是。安得有许多事耶。
之天理而已。至如些子机关及些子利害。初无一毫萌于其中。夫如是。安得有许多事耶。答赵彦休中庸问目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许东阳云程子兼举动静而言。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而言。未发即静也。是何不偏之中。为动静。而不偏不倚之中。不能兼动静耶。
中庸之中。本兼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言者也。不偏不倚。是静时中。无过不及。是动时中。而程子之于此中。但以不偏言之。则是其意必兼动静者。谓未发之中。亦此不偏。已发之中。亦此不偏。而遂曰不偏之谓中。此不偏之中。所以为兼动静言者也。乃若朱子之于此中。则其解得比程子不啻较明。既以不偏不倚为静时之中。以无过不及为动时之中矣。是其动时之无过不及。固由于静时之不偏倚者。有以致之。然既分发未发境界。而以不偏倚属之于静时。则又安得更属之于动时。而使无过不及者。为悬疣附赘之归耶。此不偏不倚之中。所以不能兼动静而言者也。然善观之则二说未始不相通。谓无过不及为不偏。亦何不可之有耶。但不如朱子解为说得尽耳。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5L 页
 择中庸之择字。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于其偏与倚之间。以审其德。于其过不及之间。以求众理。而非谓中庸之德。有一毫可择之事也。
择中庸之择字。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于其偏与倚之间。以审其德。于其过不及之间。以求众理。而非谓中庸之德。有一毫可择之事也。择乎中庸。章句谓辨别众理非他。即善之两端是也。这两端虽皆善矣。而以其非中也。故就加辨别。必求其中而用之。若既得其中。复奚事于择哉。又此所谓中。只是无过不及之中。故恐其有过不及之患。而于是乎有择之之道。乃若所谓不偏不倚之中。方当戒惧之际。此心寂然。其中之所存者。自然如此耳。有何可择于其间哉。必须熟玩章句训释。以得经文本旨。至可至可。
大舜之知。颜子之仁。与五性之仁知有异。盖五性之仁知。以本体而言。舜颜之仁知。以用工后事而言耶。
五常之知仁以性言。舜颜之知仁以心言。不曰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乎。且如舜颜之知仁。是据成德者言之。以示所以知此道者是知。所以体此道者是仁。而使学者由是以用工。盖必致此心之知识。然后可以知此道。存此心之德性。然后可以体此道故也。然及其成德之后。则此知仁。却与五常之知仁。吻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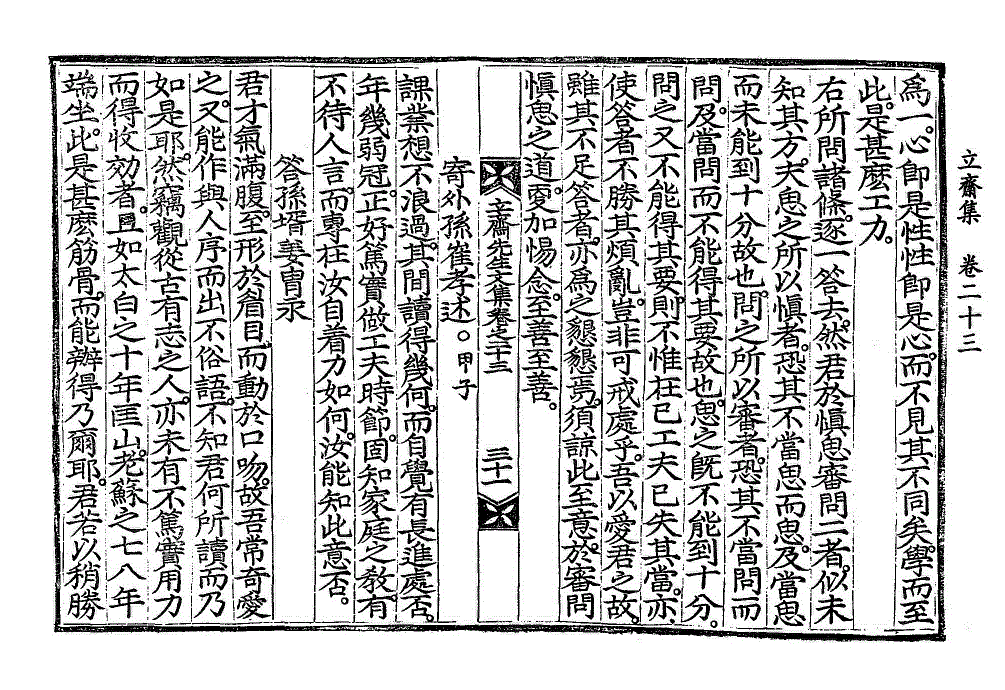 为一。心即是性性即是心。而不见其不同矣。学而至此。是甚么工力。
为一。心即是性性即是心。而不见其不同矣。学而至此。是甚么工力。右所问诸条。逐一答去。然君于慎思审问二者。似未知其方。夫思之所以慎者。恐其不当思而思。及当思而未能到十分故也。问之所以审者。恐其不当问而问。及当问而不能得其要故也。思之既不能到十分。问之又不能得其要。则不惟在己工夫已失其当。亦使答者不胜其烦乱。岂非可戒处乎。吾以爱君之故。虽其不足答者。亦为之恳恳焉。须谅此至意。于审问慎思之道。更加惕念。至善至善。
寄外孙崔孝述(甲子)
课业想不浪过。其间读得几何。而自觉有长进处否。年几弱冠。正好笃实做工夫时节。固知家庭之教。有不待人言。而专在汝自着力如何。汝能知此意否。
答孙婿姜胄永
君才气满腹。至形于眉目。而动于口吻。故吾常奇爱之。又能作与人序而出不俗语。不知君何所读而乃如是耶。然窃观从古有志之人。亦未有不笃实用力而得收效者。且如太白之十年匡山。老苏之七八年端坐。此是甚么筋骨。而能办得乃尔耶。君若以稍胜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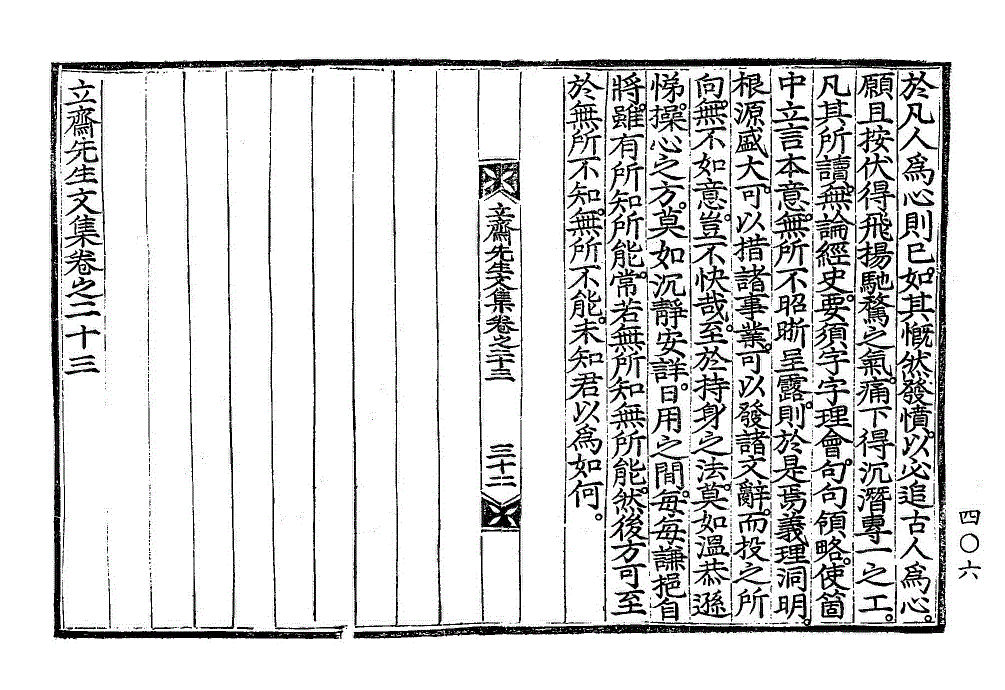 于凡人为心则已。如其慨然发愤。以必追古人为心。愿且按伏得飞扬驰骛之气。痛下得沉潜专一之工。凡其所读。无论经史。要须字字理会。句句领略。使个中立言本意。无所不昭晢呈露。则于是焉义理洞明。根源盛大。可以措诸事业。可以发诸文辞。而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岂不快哉。至于持身之法。莫如温恭逊悌。操心之方。莫如沉静安详。日用之间。每每谦挹自将。虽有所知所能。常若无所知无所能。然后方可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未知君以为如何。
于凡人为心则已。如其慨然发愤。以必追古人为心。愿且按伏得飞扬驰骛之气。痛下得沉潜专一之工。凡其所读。无论经史。要须字字理会。句句领略。使个中立言本意。无所不昭晢呈露。则于是焉义理洞明。根源盛大。可以措诸事业。可以发诸文辞。而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岂不快哉。至于持身之法。莫如温恭逊悌。操心之方。莫如沉静安详。日用之间。每每谦挹自将。虽有所知所能。常若无所知无所能。然后方可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未知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