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x 页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书
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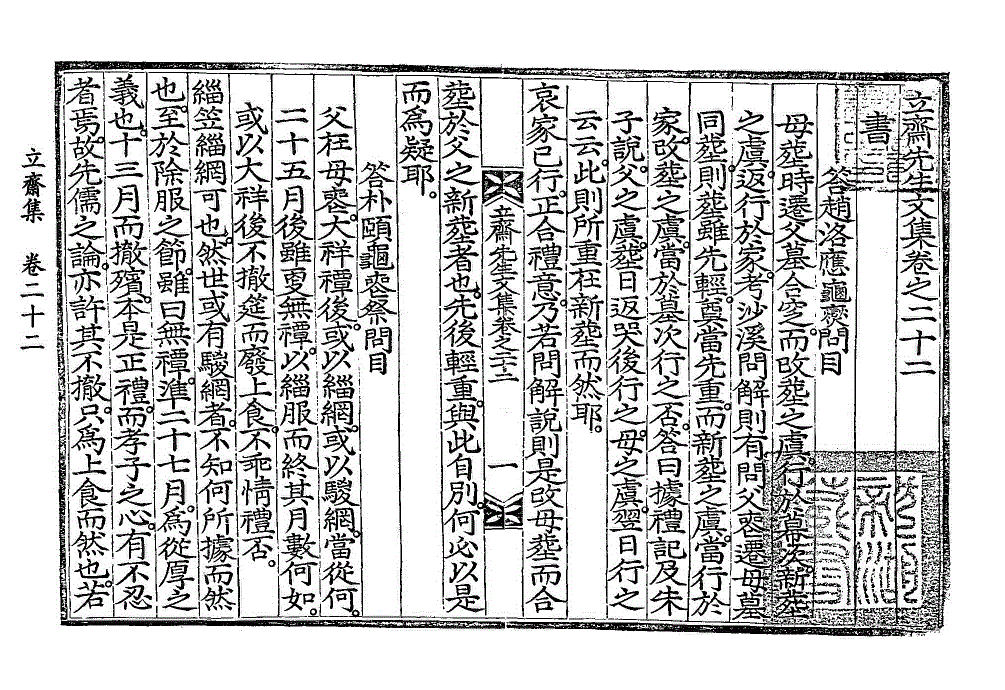 答赵洛应龟燮问目
答赵洛应龟燮问目母葬时迁父墓合窆。而改葬之虞。行于幕次。新葬之虞。返行于家。考沙溪问解则有问父丧迁母墓同葬。则葬虽先轻。奠当先重。而新葬之虞。当行于家。改葬之虞。当于墓次行之否。答曰据礼记及朱子说。父之虞。葬日返哭后行之。母之虞。翌日行之云云。此则所重在新葬而然耶。
哀家已行。正合礼意。乃若问解说则是改母葬而合葬于父之新葬者也。先后轻重。与此自别。何必以是而为疑耶。
答朴颐龟丧祭问目
父在母丧。大祥禫后。或以缁网。或以騣网。当从何。二十五月后虽更无禫。以缁服而终其月数何如。或以大祥后不撤筵而废上食。不乖情礼否。
缁笠缁网可也。然世或有騣网者。不知何所据而然也。至于除服之节。虽曰无禫。准二十七月。为从厚之义也。十三月而撤殡。本是正礼。而孝子之心。有不忍者焉。故先儒之论。亦许其不撤。只为上食而然也。若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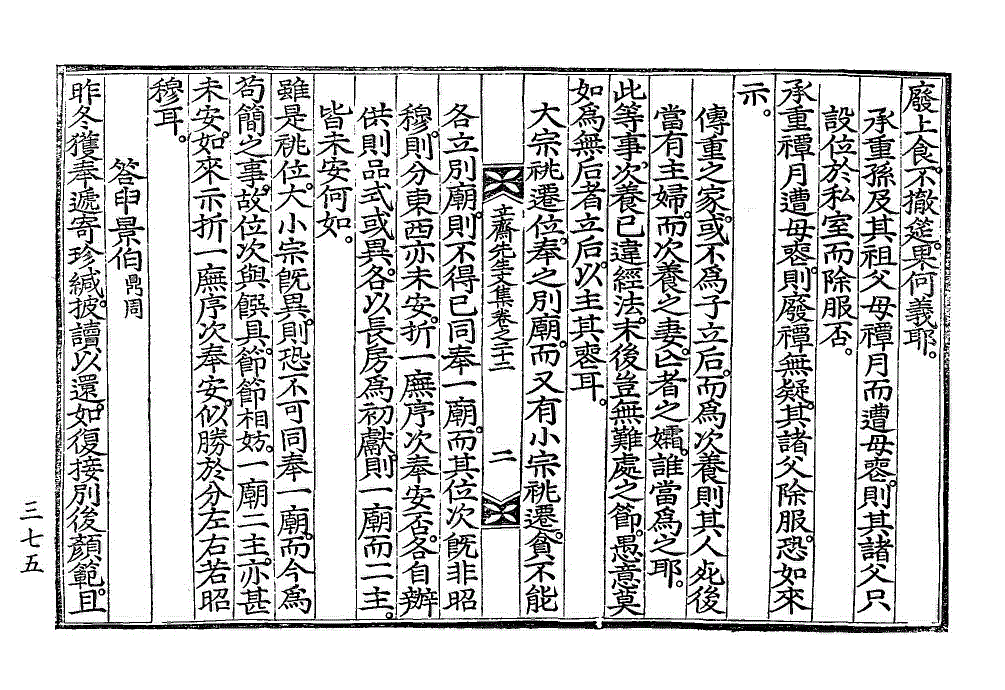 废上食。不撤筵。果何义耶。
废上食。不撤筵。果何义耶。承重孙及其祖父母禫月而遭母丧。则其诸父只设位于私室而除服否。
承重禫月遭母丧。则废禫无疑。其诸父除服。恐如来示。
传重之家。或不为子立后。而为次养则其人死后当有主妇。而次养之妻。亡者之孀。谁当为之耶。
此等事。次养已违经法。末后岂无难处之节。愚意莫如为无后者立后。以主其丧耳。
大宗祧迁位。奉之别庙。而又有小宗祧迁。贫不能各立别庙。则不得已同奉一庙。而其位次既非昭穆。则分东西亦未安。折一庑序次奉安否。各自办供则品式或异。各以长房为初献。则一庙而二主。皆未安何如。
虽是祧位。大小宗既异。则恐不可同奉一庙。而今为苟简之事。故位次与馔具。节节相妨。一庙二主。亦甚未安。如来示折一庑序次奉安。似胜于分左右若昭穆耳。
答申景伯(鼎周)
昨冬获奉递寄珍缄。披读以还。如复接别后颜范。且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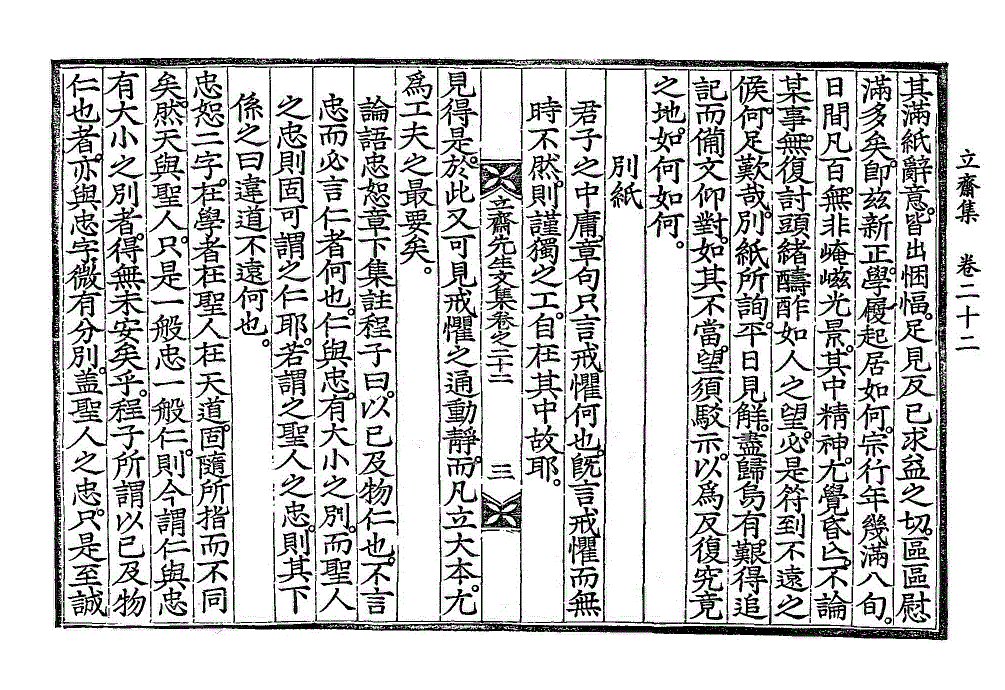 其满纸辞意。皆出悃愊。足见反己求益之切。区区慰满多矣。即玆新正。学履起居如何。宗行年几满八旬。日间凡百。无非崦嵫光景。其中精神。尤觉昏亡。不论某事。无复讨头绪酬酢如人之望。必是符到不远之候。何足叹哉。别纸所询。平日见解。尽归乌有。艰得追记而备文仰对。如其不当。望须驳示。以为反复究竟之地。如何如何。
其满纸辞意。皆出悃愊。足见反己求益之切。区区慰满多矣。即玆新正。学履起居如何。宗行年几满八旬。日间凡百。无非崦嵫光景。其中精神。尤觉昏亡。不论某事。无复讨头绪酬酢如人之望。必是符到不远之候。何足叹哉。别纸所询。平日见解。尽归乌有。艰得追记而备文仰对。如其不当。望须驳示。以为反复究竟之地。如何如何。别纸
君子之中庸。章句只言戒惧何也。既言戒惧而无时不然。则谨独之工。自在其中故耶。
见得是。于此又可见戒惧之通动静。而凡立大本。尤为工夫之最要矣。
论语忠恕章下集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不言忠而必言仁者何也。仁与忠。有大小之别。而圣人之忠则固可谓之仁耶。若谓之圣人之忠。则其下系之曰违道不远何也。
忠恕二字。在学者在圣人在天道。固随所指而不同矣。然天与圣人。只是一般忠一般仁。则今谓仁与忠有大小之别者。得无未安矣乎。程子所谓以己及物仁也者。亦与忠字微有分别。盖圣人之忠。只是至诚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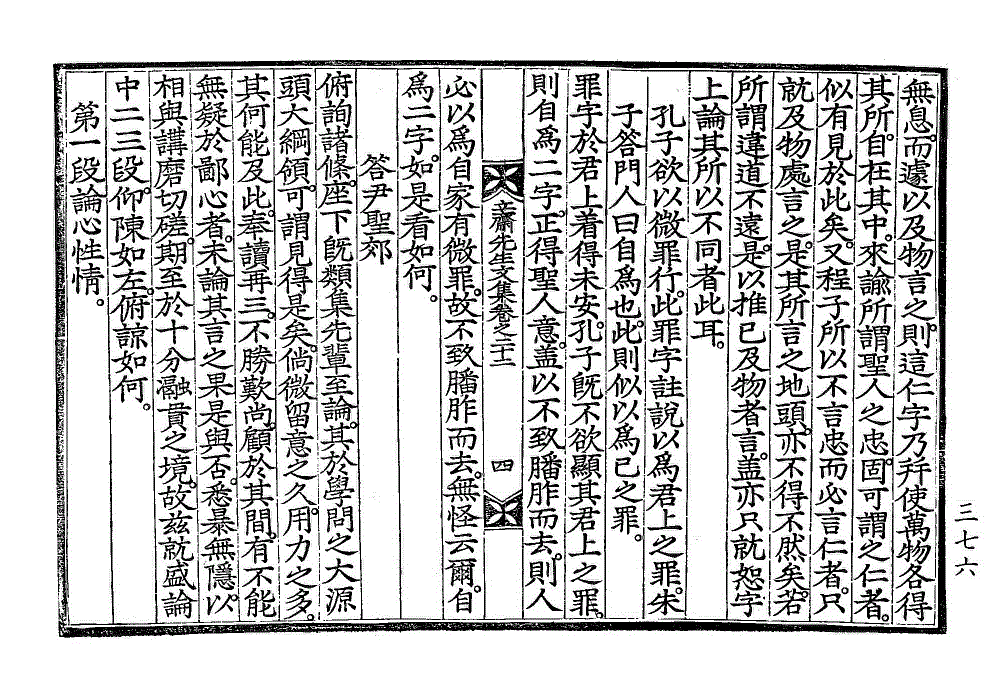 无息。而遽以及物言之。则这仁字乃并使万物各得其所。自在其中。来谕所谓圣人之忠。固可谓之仁者。似有见于此矣。又程子所以不言忠而必言仁者。只就及物处言之。是其所言之地头。亦不得不然矣。若所谓违道不远。是以推己及物者言。盖亦只就恕字上论其所以不同者此耳。
无息。而遽以及物言之。则这仁字乃并使万物各得其所。自在其中。来谕所谓圣人之忠。固可谓之仁者。似有见于此矣。又程子所以不言忠而必言仁者。只就及物处言之。是其所言之地头。亦不得不然矣。若所谓违道不远。是以推己及物者言。盖亦只就恕字上论其所以不同者此耳。孔子欲以微罪行。此罪字注说以为君上之罪。朱子答门人曰自为也。此则似以为己之罪。
罪字于君上着得未安。孔子既不欲显其君上之罪。则自为二字。正得圣人意。盖以不致膰胙而去。则人必以为自家有微罪。故不致膰胙而去。无怪云尔。自为二字。如是看如何。
答尹圣郊
俯询诸条。座下既类集先辈至论。其于学问之大源头大纲领。可谓见得是矣。倘微留意之久。用力之多。其何能及此。奉读再三。不胜叹尚。顾于其间。有不能无疑于鄙心者。未论其言之果是与否。悉暴无隐。以相与讲磨切磋。期至于十分融贯之境。故玆就盛论中二三段。仰陈如左。俯谅如何。
第一段论心性情。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7H 页
 所论大槩得之。但人心之所以必曰危。以其生于形气之私而易流于人欲故耳。今谓须臾或放而易入于危者。是将人下工夫处。参入为说。道心之所以必曰微。以其原于性命之正。而其发也微妙难见故耳。今谓毫芒或失则必至于微者。是亦将人下工夫处。参入为说。俱非当初所以只就人道心上平论其理之意。又四端固纯善无恶。而七情则是兼善恶者。故其发也气若听命于理则斯中其节而无不善。今谓气全用事。理不能使气。故不得中节而为恶。则是以七情为纯恶而无善矣。得无未安矣乎。至如心之一字。程朱之论。发明已尽。性犹太极。心犹阴阳者。又是朱子之说。大学或问亦曰惟人之生。得其气之正且通者。故其性为最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澈。万理咸备。或者之以心专属于气者。似本于此。又须先见得此心是合理气统性情底物事分明。然后方无流于一偏之患。彼释氏之以作用为性者。是徒知心之为气。而不知理在其中者。有仁义礼智之性故也。阳明之以致良知为学者。是徒知心之有理。而不知气之在其中者。有清浊粹驳之异故也。子思所谓喜怒哀乐。是浑沦言之者。故就其中拈出善底以为四者。然
所论大槩得之。但人心之所以必曰危。以其生于形气之私而易流于人欲故耳。今谓须臾或放而易入于危者。是将人下工夫处。参入为说。道心之所以必曰微。以其原于性命之正。而其发也微妙难见故耳。今谓毫芒或失则必至于微者。是亦将人下工夫处。参入为说。俱非当初所以只就人道心上平论其理之意。又四端固纯善无恶。而七情则是兼善恶者。故其发也气若听命于理则斯中其节而无不善。今谓气全用事。理不能使气。故不得中节而为恶。则是以七情为纯恶而无善矣。得无未安矣乎。至如心之一字。程朱之论。发明已尽。性犹太极。心犹阴阳者。又是朱子之说。大学或问亦曰惟人之生。得其气之正且通者。故其性为最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澈。万理咸备。或者之以心专属于气者。似本于此。又须先见得此心是合理气统性情底物事分明。然后方无流于一偏之患。彼释氏之以作用为性者。是徒知心之为气。而不知理在其中者。有仁义礼智之性故也。阳明之以致良知为学者。是徒知心之有理。而不知气之在其中者。有清浊粹驳之异故也。子思所谓喜怒哀乐。是浑沦言之者。故就其中拈出善底以为四者。然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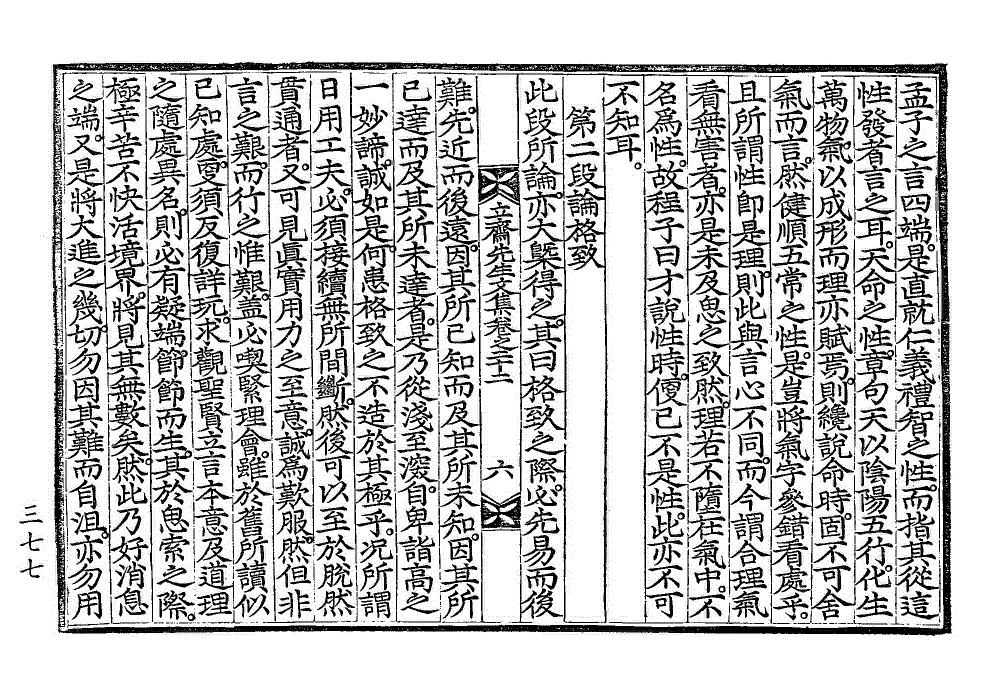 孟子之言四端。是直就仁义礼智之性。而指其从这性发者言之耳。天命之性。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则才说命时。固不可舍气而言。然健顺五常之性。是岂将气字参错看处乎。且所谓性即是理。则此与言心不同。而今谓合理气看无害者。亦是未及思之致然。理若不堕在气中。不名为性。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亦不可不知耳。
孟子之言四端。是直就仁义礼智之性。而指其从这性发者言之耳。天命之性。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则才说命时。固不可舍气而言。然健顺五常之性。是岂将气字参错看处乎。且所谓性即是理。则此与言心不同。而今谓合理气看无害者。亦是未及思之致然。理若不堕在气中。不名为性。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亦不可不知耳。第二段论格致。
此段所论。亦大槩得之。其曰格致之际。必先易而后难。先近而后远。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者。是乃从浅至深。自卑诣高之一妙谛。诚如是。何患格致之不造于其极乎。况所谓日用工夫。必须接续无所间断。然后可以至于脱然贯通者。又可见真实用力之至意。诚为叹服。然但非言之艰。而行之惟艰。盖必吃紧理会。虽于旧所读似已知处。更须反复详玩。求观圣贤立言本意及道理之随处异名。则必有疑端。节节而生。其于思索之际。极辛苦不快活境界。将见其无数矣。然此乃好消息之端。又是将大进之几。切勿因其难而自沮。亦勿用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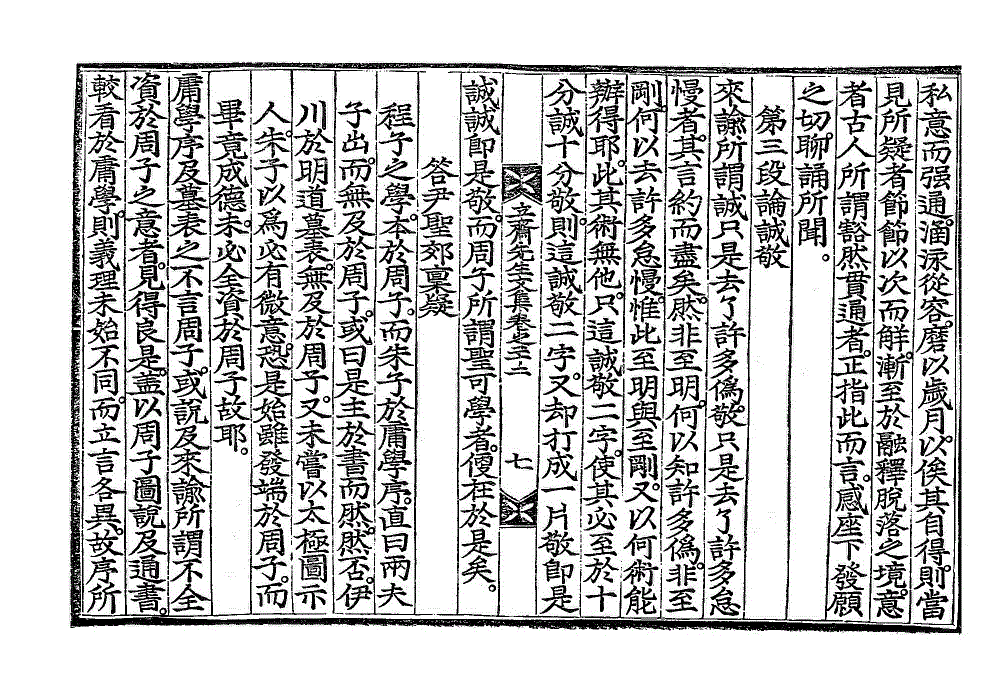 私意而强通。涵泳从容。磨以岁月。以俟其自得。则当见所疑者节节以次而解。渐至于融释脱落之境。意者古人所谓豁然贯通者。正指此而言。感座下发愿之切。聊诵所闻。
私意而强通。涵泳从容。磨以岁月。以俟其自得。则当见所疑者节节以次而解。渐至于融释脱落之境。意者古人所谓豁然贯通者。正指此而言。感座下发愿之切。聊诵所闻。第三段论诚敬。
来谕所谓诚只是去了许多伪。敬只是去了许多怠慢者。其言约而尽矣。然非至明。何以知许多伪。非至刚。何以去许多怠慢。惟此至明与至刚。又以何术能办得耶。此其术无他。只这诚敬二字。使其必至于十分诚十分敬。则这诚敬二字。又却打成一片敬即是诚诚即是敬。而周子所谓圣可学者。便在于是矣。
答尹圣郊禀疑
程子之学。本于周子。而朱子于庸学序。直曰两夫子出。而无及于周子。或曰是主于书而然。然否。伊川于明道墓表。无及于周子。又未尝以太极图示人。朱子以为必有微意。恐是始虽发端于周子。而毕竟成德。未必全资于周子故耶。
庸学序及墓表之不言周子。或说及来谕所谓不全资于周子之意者。见得良是。盖以周子图说及通书。较看于庸学。则义理未始不同。而立言各异。故序所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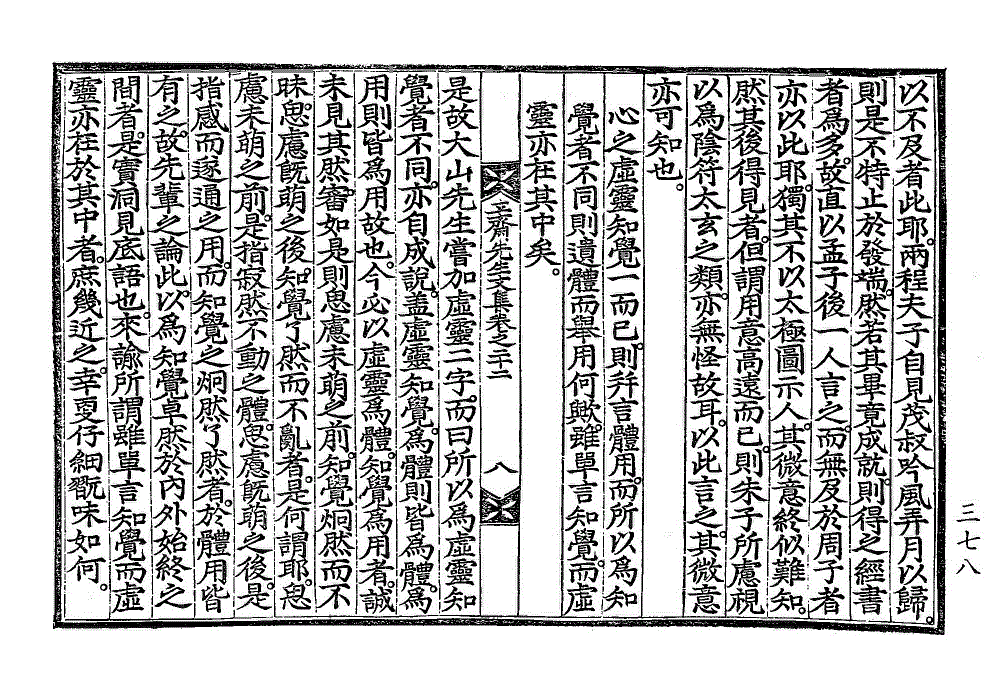 以不及者此耶。两程夫子自见茂叔吟风弄月以归。则是不特止于发端。然若其毕竟成就。则得之经书者为多。故直以孟子后一人言之。而无及于周子者亦以此耶。独其不以太极图示人。其微意终似难知。然其后得见者。但谓用意高远而已。则朱子所虑视以为阴符太玄之类。亦无怪故耳。以此言之。其微意亦可知也。
以不及者此耶。两程夫子自见茂叔吟风弄月以归。则是不特止于发端。然若其毕竟成就。则得之经书者为多。故直以孟子后一人言之。而无及于周子者亦以此耶。独其不以太极图示人。其微意终似难知。然其后得见者。但谓用意高远而已。则朱子所虑视以为阴符太玄之类。亦无怪故耳。以此言之。其微意亦可知也。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则并言体用。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则遗体而举用何欤。虽单言知觉。而虚灵亦在其中矣。
是故大山先生尝加虚灵二字。而曰所以为虚灵知觉者不同。亦自成说。盖虚灵知觉。为体则皆为体。为用则皆为用故也。今必以虚灵为体。知觉为用者。诚未见其然。审如是则思虑未萌之前。知觉炯然而不昧。思虑既萌之后。知觉了然而不乱者。是何谓耶。思虑未萌之前。是指寂然不动之体。思虑既萌之后。是指感而遂通之用。而知觉之炯然了然者。于体用皆有之。故先辈之论此。以为知觉卓然于内外始终之间者。是实洞见底语也。来谕所谓虽单言知觉而虚灵亦在于其中者。庶几近之。幸更仔细玩味如何。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9H 页
 泰伯文王。夫子皆谓之至德。然文王则三分有二。故朱子曰泰伯又高于文王。抑至德有浅深之可言耶。
泰伯文王。夫子皆谓之至德。然文王则三分有二。故朱子曰泰伯又高于文王。抑至德有浅深之可言耶。三分有二之有字。是据当日人归而言。若文王之心则初无此有字。故率商之叛国。以服事殷。所以为至德也。若朱子所谓泰伯高于文王。特以其迹言之。至德岂有浅深之可言耶。
一士友遭大故。兄及兄之子若孙俱没。不可不用兄亡弟及之例。告文请制示焉。且其兄丧期而撤耶。祔庙当于何时。傍题书孝字何如。
既用兄亡弟及之例。则似当趁其葬时。先事告由。而并及于兄可矣。告文似当曰家兄既殁。子孙俱亡。曾孙立后。又无其望。主丧奉祀。惟子一人。礼许弟及。例有可援。玆不获已敢题主傍。变节至此。弥极痛伤。告兄则似当曰大人之丧。兄当主之。云胡不胜。又绝后焉。主丧之责。弟外无他。礼既许及。重又有在。玆以弟名。傍题奉祀。痛割之极。谨此仰告云云。如是措语。未知何如。至于兄丧既无为之三年者。则待自家服尽期而撤。因祔祖庙。既用亡及之例。则傍题书以孝字恐宜。然皆不敢质言。更询礼家而处之如何。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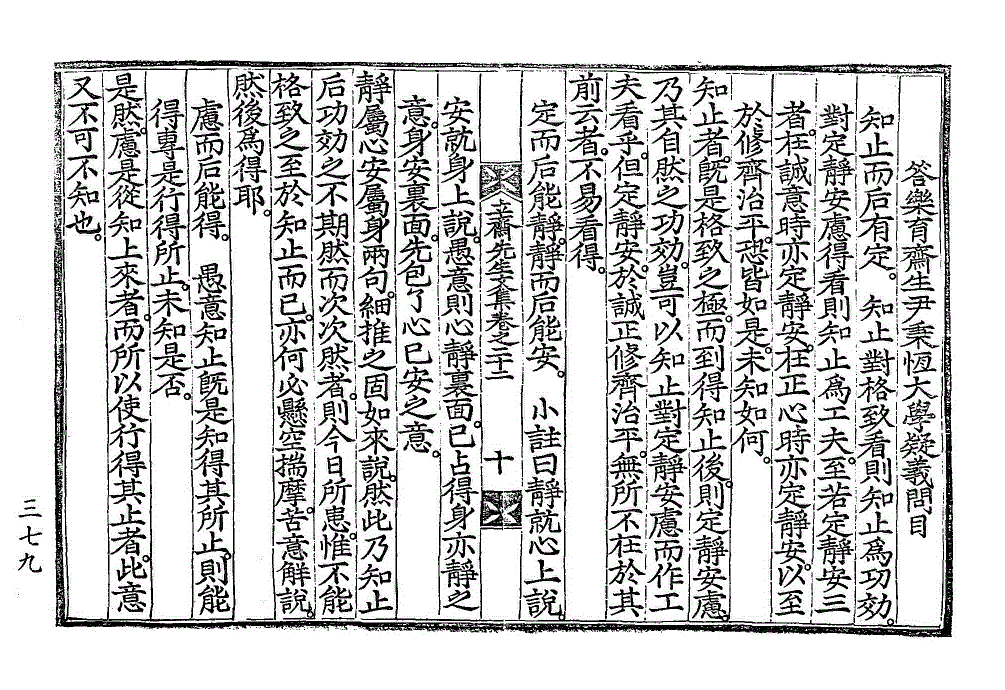 答乐育斋生尹秉恒大学疑义问目
答乐育斋生尹秉恒大学疑义问目知止而后有定。 知止对格致看则知止为功效。对定静安虑得看则知止为工夫。至若定静安三者。在诚意时亦定静安。在正心时亦定静安。以至于修齐治平。恐皆如是。未知如何。
知止者。既是格致之极。而到得知止后。则定静安虑。乃其自然之功效。岂可以知止对定静安虑而作工夫看乎。但定静安。于诚正修齐治平。无所不在于其前云者。不易看得。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小注曰静就心上说。安就身上说。愚意则心静里面。已占得身亦静之意。身安里面。先包了心已安之意。
静属心安属身两句。细推之固如来说。然此乃知止后功效之不期然而次次然者。则今日所患。惟不能格致之至于知止而已。亦何必悬空揣摩。苦意解说。然后为得耶。
虑而后能得。 愚意知止既是知得其所止。则能得专是行得所止。未知是否。
是然。虑是从知上来者。而所以使行得其止者。此意又不可不知也。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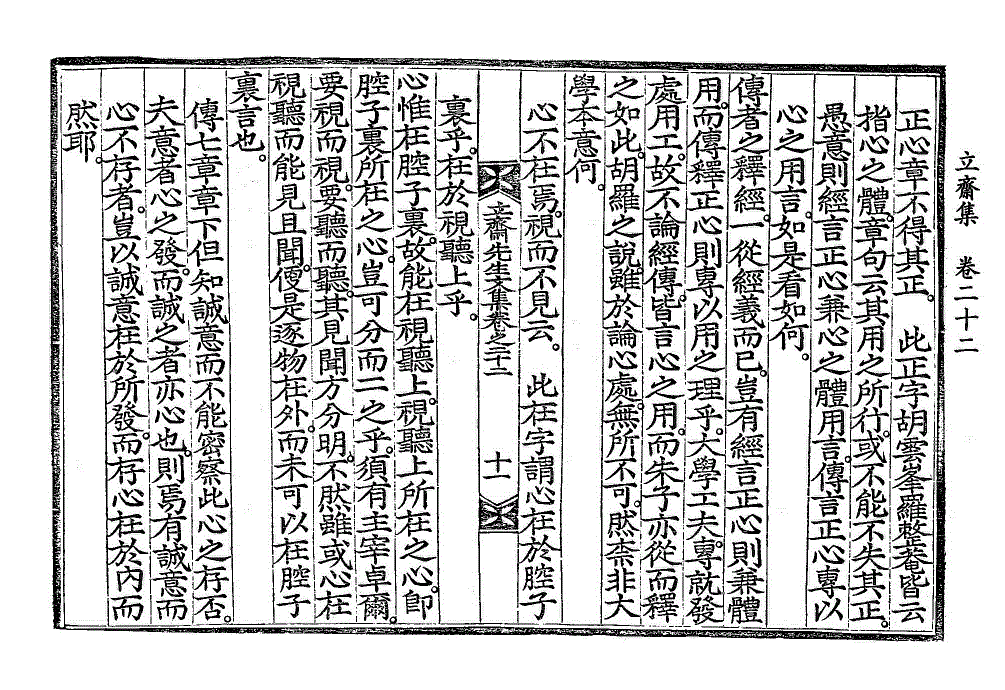 正心章不得其正。 此正字胡云峰,罗整庵皆云指心之体。章句云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愚意则经言正心兼心之体用言。传言正心专以心之用言。如是看如何。
正心章不得其正。 此正字胡云峰,罗整庵皆云指心之体。章句云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愚意则经言正心兼心之体用言。传言正心专以心之用言。如是看如何。传者之释经。一从经义而已。岂有经言正心则兼体用。而传释正心则专以用之理乎。大学工夫。专就发处用工。故不论经传。皆言心之用。而朱子亦从而释之如此。胡,罗之说。虽于论心处。无所不可。然柰非大学本意何。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云。 此在字谓心在于腔子里乎。在于视听上乎。
心惟在腔子里。故能在视听上。视听上所在之心。即腔子里所在之心。岂可分而二之乎。须有主宰卓尔。要视而视。要听而听。其见闻方分明。不然虽或心在视听而能见且闻。便是逐物在外。而未可以在腔子里言也。
传七章章下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夫意者心之发。而诚之者亦心也。则焉有诚意而心不存者。岂以诚意在于所发。而存心在于内而然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0L 页
 所谓诚其意。但令心之所发于为善去恶。得其快足而已。此譬如一带水。淘去泥沙而复其清洁。至于正心工夫。又欲此心之常存而不放。譬如水得清洁后常使之澄然恬平而不起波浪。则可以涵映万象而无毫发不照之物。此即于诚意后密察心存与否之法耳。
所谓诚其意。但令心之所发于为善去恶。得其快足而已。此譬如一带水。淘去泥沙而复其清洁。至于正心工夫。又欲此心之常存而不放。譬如水得清洁后常使之澄然恬平而不起波浪。则可以涵映万象而无毫发不照之物。此即于诚意后密察心存与否之法耳。所恶于上云云。 絜矩之道。兼言好恶。而此四句只言其所恶何也。
方于事上而好人佞己。为尉则凌守。而为守则易尉者。常人之情。大抵皆然。故此言絜矩之道。必以所恶言之者此也。然所恶既勿施。则所好之当施。自可知矣。如何如何。
心学图虚灵即体。知觉即用。而神明则体欤用欤。且心思一圈。思既心之发。则程氏之必置此于戒操之下何也。(以下心经疑义)
神者虚灵之极也。明者知觉之至也。分而言之则神与虚。知为一类。明与灵。觉为一类。而所谓知觉者。虽对虚灵而为用。然思虑未萌之时。炯然而不昧者。独非知觉乎。是则知觉亦未必不为体也。至于心思一圈之置于操存之下。元来林隐此图。但举大纲而分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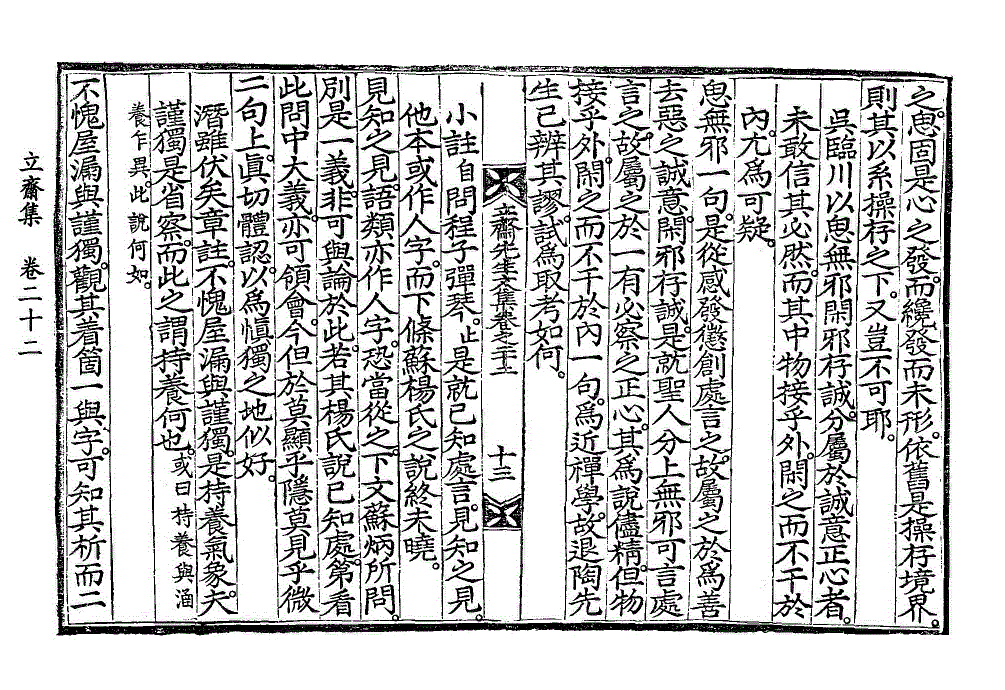 之。思固是心之发。而才发而未形。依旧是操存境界。则其以系操存之下。又岂不可耶。
之。思固是心之发。而才发而未形。依旧是操存境界。则其以系操存之下。又岂不可耶。吴临川以思无邪闲邪存诚。分属于诚意正心者。未敢信其必然。而其中物接乎外。闲之而不干于内。尤为可疑。
思无邪一句。是从感发惩创处言之。故属之于为善去恶之诚意。闲邪存诚。是就圣人分上无邪可言处言之。故属之于一有必察之正心。其为说尽精。但物接乎外。闲之而不干于内一句。为近禅学。故退陶先生已辨其谬。试为取考如何。
小注(自)问程子弹琴。(止)是就已知处言。见知之见。他本或作人字。而下条苏杨氏之说终未晓。
见知之见。语类亦作人字。恐当从之。下文苏炳所问。别是一义。非可与论于此。若其杨氏说已知处。第看此问中大义。亦可领会。今但于莫显乎隐莫见乎微二句上。真切体认。以为慎独之地似好。
潜虽伏矣章注。不愧屋漏与谨独。是持养气象。夫谨独是省察。而此之谓持养何也。(或曰持养与涵养乍异。此说何如。)
不愧屋漏与谨独。观其着个一与字。可知其析而二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1L 页
 之矣。但其语势短促。未易看出。故朱子于中庸或问已详言之。何得谓此一句之通为一事耶。持养二字虽与存养一般。而元来戒惧之以存养言者。朱子以为通动静统体工夫。则今并谨独而谓持养气象者。不亦宜乎。至于涵养。退溪以为兼动静而观。其造语匹似属静意多。今谓与持养乍异者。看得尽孜细。
之矣。但其语势短促。未易看出。故朱子于中庸或问已详言之。何得谓此一句之通为一事耶。持养二字虽与存养一般。而元来戒惧之以存养言者。朱子以为通动静统体工夫。则今并谨独而谓持养气象者。不亦宜乎。至于涵养。退溪以为兼动静而观。其造语匹似属静意多。今谓与持养乍异者。看得尽孜细。所谓修身章附注第九条。撑船须用篙。吃饭须使匙。未知篙与匙。指心而言耶。指敬而言耶。
既曰心者身之主。而继之以此二句。其下又曰不理会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谓。则所谓篙与匙。固以此心言之。然此心之所以能为一身之主者。敬而已。恐未可二视之也。
乐记礼乐章附注李端伯条言不庄不敬云云。窃意养心只有敬字工夫。而敬之用工。自言貌上先耶。
是然。言貌不庄敬则心亦不能和乐。盖和乐者。虽其得之之极于深至。而终是庄敬得外面者。为之防范故耳。
廖晋卿条。先举辨奸论而继言淳叟事者。意谓淳叟之独去打坐。亦不近人情。且答晋卿读书之问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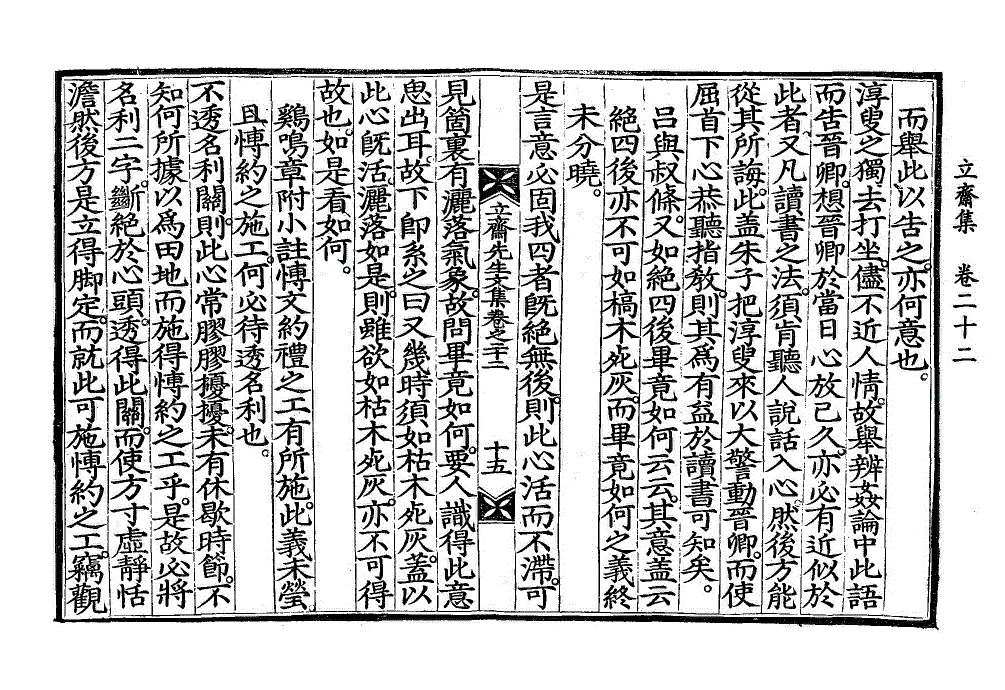 而举此以告之。亦何意也。
而举此以告之。亦何意也。淳叟之独去打坐。尽不近人情。故举辨奸论中此语而告晋卿。想晋卿于当日心放已久。亦必有近似于此者。又凡读书之法。须肯听人说话入心。然后方能从其所诲。此盖朱子把淳叟来以大警动晋卿。而使屈首下心恭听指教。则其为有益于读书可知矣。
吕与叔条。又如绝四后毕竟如何云云。其意盖云绝四后亦不可如槁木死灰。而毕竟如何之义终未分晓。
是言意必固我四者既绝无后。则此心活而不滞。可见个里有洒落气象。故问毕竟如何。要人识得此意思出耳。故下即系之曰又几时须如枯木死灰。盖以此心既活。洒落如是。则虽欲如枯木死灰。亦不可得故也。如是看如何。
鸡鸣章附小注博文约礼之工有所施。此义未莹。且博约之施工。何必待透名利也。
不透名利关。则此心常胶胶扰扰。未有休歇时节。不知何所据以为田地而施得博约之工乎。是故必将名利二字。断绝于心头。透得此关。而使方寸虚静恬澹然后方是立得脚定。而就此可施博约之工。窃观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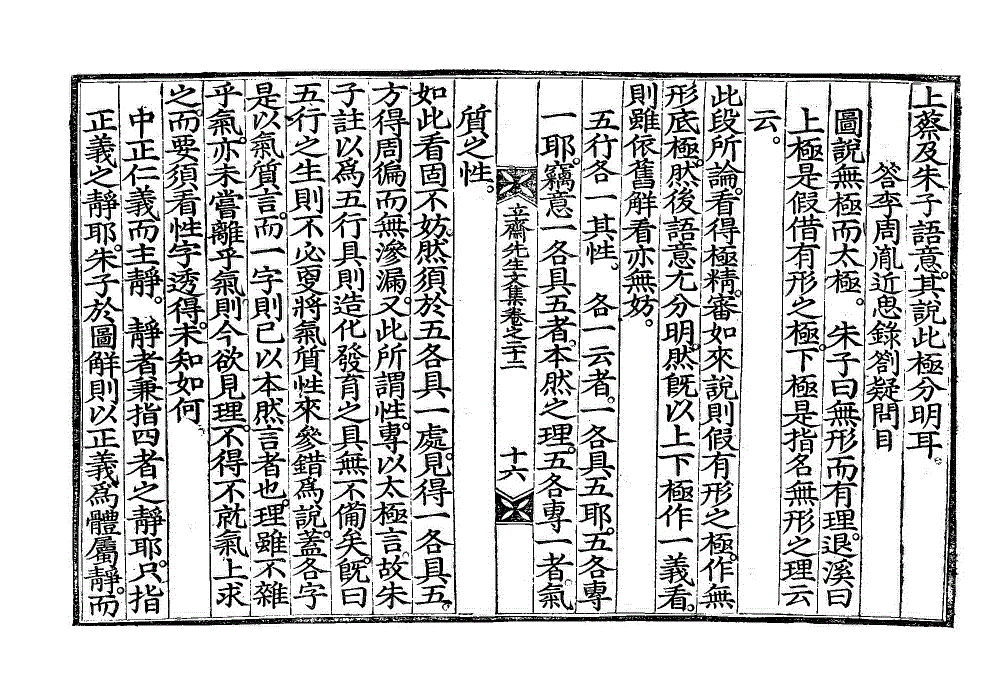 上蔡及朱子语意。其说此极分明耳。
上蔡及朱子语意。其说此极分明耳。答李周胤近思录劄疑问目
图说无极而太极。 朱子曰无形而有理。退溪曰上极是假借有形之极。下极是指名无形之理云云。
此段所论。看得极精。审如来说则假有形之极。作无形底极。然后语意尤分明。然既以上下极作一义看。则虽依旧解看亦无妨。
五行各一其性。 各一云者。一各具五耶。五各专一耶。窃意一各具五者。本然之理。五各专一者。气质之性。
如此看固不妨。然须于五各具一处。见得一各具五。方得周遍而无渗漏。又此所谓性。专以太极言。故朱子注以为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既曰五行之生则不必更将气质性来参错为说。盖各字是以气质言。而一字则已以本然言者也。理虽不杂乎气。亦未尝离乎气。则今欲见理。不得不就气上求之。而要须看性字透得。未知如何。
中正仁义而主静。 静者兼指四者之静耶。只指正义之静耶。朱子于图解则以正义为体属静。而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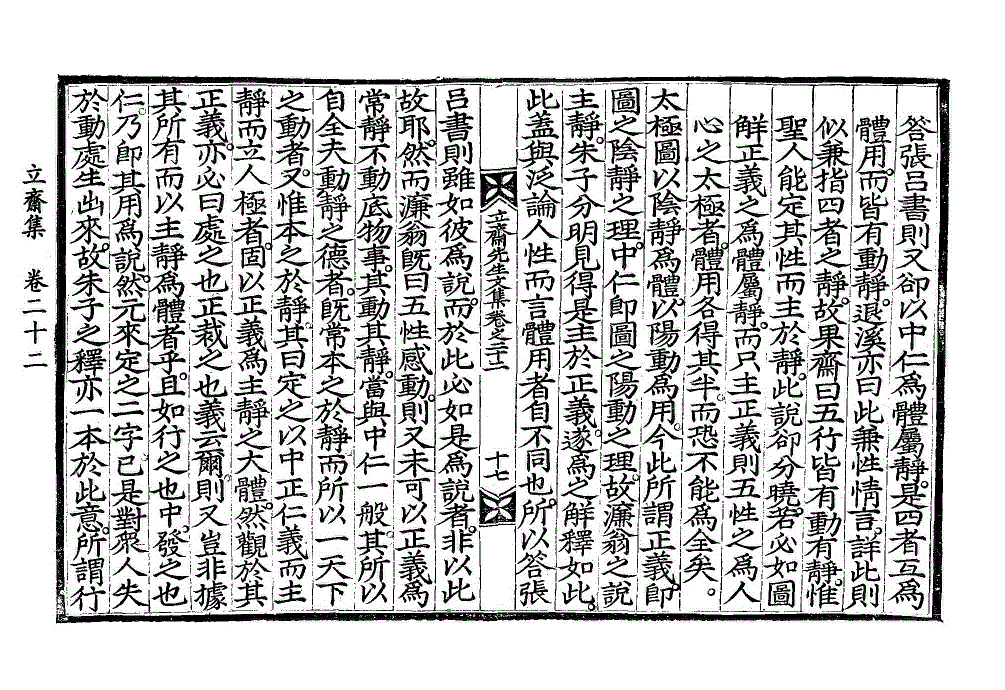 答张吕书则又却以中仁为体属静。是四者互为体用。而皆有动静。退溪亦曰此兼性情言。详此则似兼指四者之静。故果斋曰五行皆有动有静。惟圣人能定其性而主于静。此说却分晓。若必如图解正义之为体属静。而只主正义则五性之为人心之太极者。体用各得其半。而恐不能为全矣。
答张吕书则又却以中仁为体属静。是四者互为体用。而皆有动静。退溪亦曰此兼性情言。详此则似兼指四者之静。故果斋曰五行皆有动有静。惟圣人能定其性而主于静。此说却分晓。若必如图解正义之为体属静。而只主正义则五性之为人心之太极者。体用各得其半。而恐不能为全矣。太极图以阴静为体。以阳动为用。今此所谓正义。即图之阴静之理。中仁即图之阳动之理。故濂翁之说主静。朱子分明见得是主于正义。遂为之解释如此。此盖与泛论人性而言体用者自不同也。所以答张吕书则虽如彼为说。而于此必如是为说者。非以此故耶。然而濂翁既曰五性感动。则又未可以正义为常静不动底物事。其动其静。当与中仁一般。其所以自全夫动静之德者。既常本之于静。而所以一天下之动者。又惟本之于静。其曰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而立人极者。固以正义为主静之大体。然观于其正义。亦必曰处之也正裁之也义云尔。则又岂非据其所有而以主静为体者乎。且如行之也中。发之也仁。乃即其用为说。然元来定之二字。已是对众人失于动处生出来。故朱子之释亦一本于此意。所谓行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3L 页
 之处之发之裁之云者。无非所以体贴定之二字而为说者也。且以图象观之则阴静之中。已有阳动之理。即中之白是已。阳动之中已有阴静之理。即中之黑是已。以此推之。正义之中。已含中仁。中仁之中。已含正义。虽曰正义为体而体未尝不具。夫四者虽曰中仁为用。而用未尝不具。夫四者元未有得其半失其半之理。未知如此看如何。
之处之发之裁之云者。无非所以体贴定之二字而为说者也。且以图象观之则阴静之中。已有阳动之理。即中之白是已。阳动之中已有阴静之理。即中之黑是已。以此推之。正义之中。已含中仁。中仁之中。已含正义。虽曰正义为体而体未尝不具。夫四者虽曰中仁为用。而用未尝不具。夫四者元未有得其半失其半之理。未知如此看如何。西铭。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语类云大君以上。凡言一体。于时保之以下。方是下手处。此棋盘着棋之别也。然则曰尊曰慈曰长。其曰幼吾者。于一体中已有下工意何也。岂以长幼分殊处。尤不可以不严。故特寓亲仁差等之意耶。
此二句。只是论其理当如是而已。然必于长幼上而云然者。如来说看无妨耶。且不独于棋盘处有此二句。于着棋处亦有。只论其理者。如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二句是也。盖一体与下工。元自相贯。故各有此等句于其中。要在人领会将去耳。
浮图明鬼云云。 一出于佛氏之门。语类诐淫邪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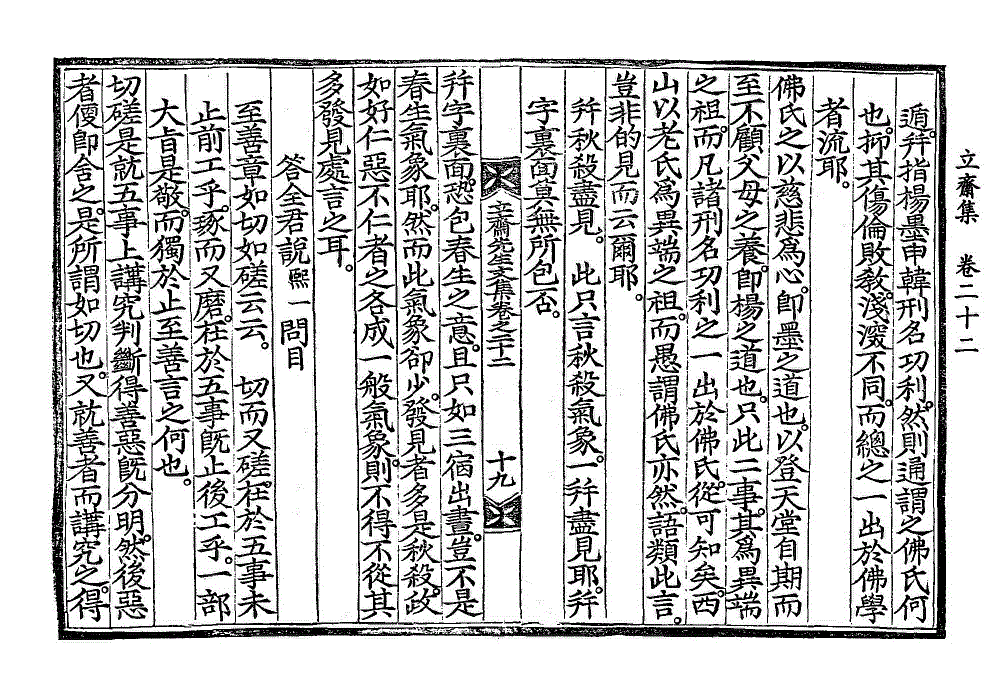 遁。并指杨墨申韩刑名功利。然则通谓之佛氏何也。抑其伤伦败教。浅深不同。而总之一出于佛学者流耶。
遁。并指杨墨申韩刑名功利。然则通谓之佛氏何也。抑其伤伦败教。浅深不同。而总之一出于佛学者流耶。佛氏之以慈悲为心。即墨之道也。以登天堂自期而至不顾父母之养。即杨之道也。只此二事。其为异端之祖。而凡诸刑名功利之一出于佛氏。从可知矣。西山以老氏为异端之祖。而愚谓佛氏亦然。语类此言。岂非的见而云尔耶。
并秋杀尽见。 此只言秋杀气象。一并尽见耶。并字里面莫无所包否。
并字里面。恐包春生之意。且只如三宿出昼。岂不是春生气象耶。然而此气象却少。发见者多是秋杀。政如好仁恶不仁者之各成一般气象。则不得不从其多发见处言之耳。
答全君说(熙一)问目
至善章如切如磋云云。 切而又磋。在于五事未止前工乎。琢而又磨。在于五事既止后工乎。一部大旨是敬。而独于止至善言之何也。
切磋是就五事上讲究判断得善恶既分明。然后恶者便即舍之。是所谓如切也。又就善者而讲究之。得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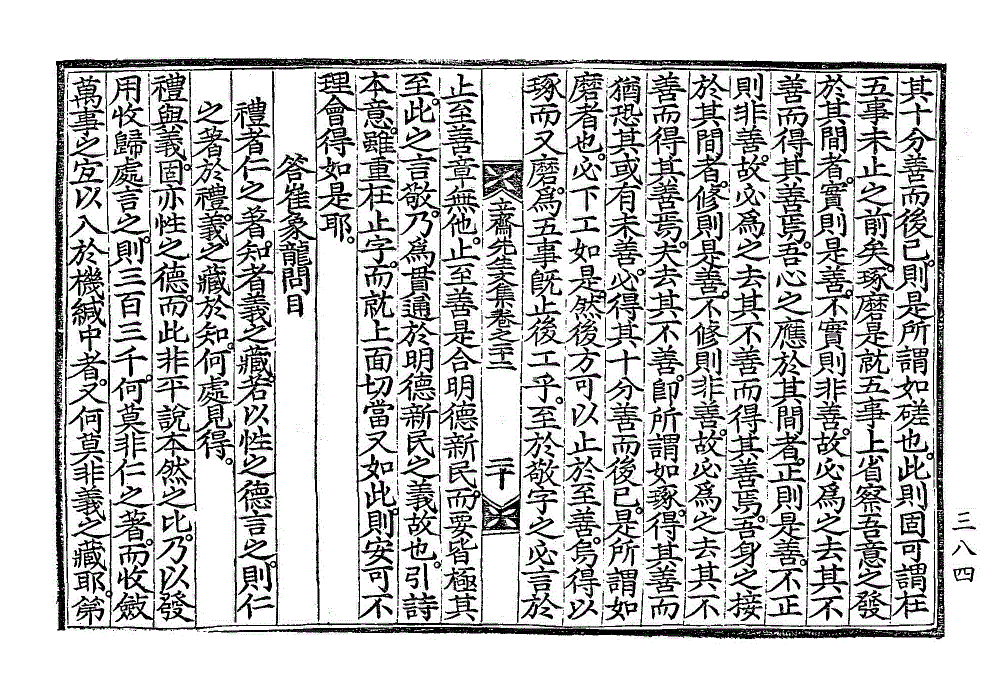 其十分善而后已。则是所谓如磋也。此则固可谓在五事未止之前矣。琢磨是就五事上省察吾意之发于其间者。实则是善。不实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吾心之应于其间者。正则是善。不正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吾身之接于其间者。修则是善。不修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夫去其不善。即所谓如琢。得其善而犹恐其或有未善。必得其十分善而后已。是所谓如磨者也。必下工如是。然后方可以止于至善。乌得以琢而又磨。为五事既止后工乎。至于敬字之必言于止至善章无他。止至善是合明德新民。而要皆极其至。此之言敬。乃为贯通于明德新民之义故也。引诗本意。虽重在止字。而就上面切当又如此。则安可不理会得如是耶。
其十分善而后已。则是所谓如磋也。此则固可谓在五事未止之前矣。琢磨是就五事上省察吾意之发于其间者。实则是善。不实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吾心之应于其间者。正则是善。不正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吾身之接于其间者。修则是善。不修则非善。故必为之去其不善而得其善焉。夫去其不善。即所谓如琢。得其善而犹恐其或有未善。必得其十分善而后已。是所谓如磨者也。必下工如是。然后方可以止于至善。乌得以琢而又磨。为五事既止后工乎。至于敬字之必言于止至善章无他。止至善是合明德新民。而要皆极其至。此之言敬。乃为贯通于明德新民之义故也。引诗本意。虽重在止字。而就上面切当又如此。则安可不理会得如是耶。答崔象龙问目
礼者仁之著。知者义之藏。若以性之德言之。则仁之著于礼。义之藏于知。何处见得。
礼与义。固亦性之德。而此非平说本然之比。乃以发用收归处言之。则三百三千。何莫非仁之著。而收敛万事之宜以入于机缄中者。又何莫非义之藏耶。第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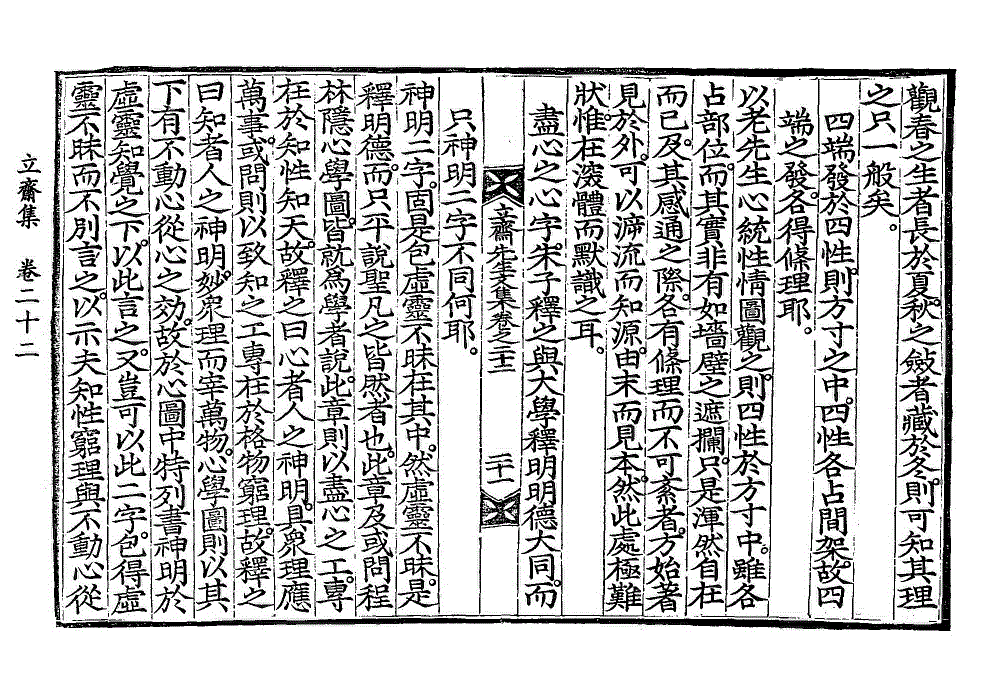 观春之生者长于夏。秋之敛者藏于冬。则可知其理之只一般矣。
观春之生者长于夏。秋之敛者藏于冬。则可知其理之只一般矣。四端发于四性。则方寸之中。四性各占间架。故四端之发。各得条理耶。
以老先生心统性情图观之。则四性于方寸中。虽各占部位。而其实非有如墙壁之遮拦。只是浑然自在而已。及其感通之际。各有条理而不可紊者。方始著见于外。可以溯流而知源。由末而见本。然此处极难状。惟在深体而默识之耳。
尽心之心字。朱子释之与大学释明明德大同。而只神明二字不同何耶。
神明二字。固是包虚灵不昧在其中。然虚灵不昧。是释明德。而只平说圣凡之皆然者也。此章及或问程林隐心学图。皆就为学者说。此章则以尽心之工。专在于知性知天。故释之曰心者人之神明。具众理应万事。或问则以致知之工专在于格物穷理。故释之曰知者人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心学图则以其下有不动心从心之效。故于心图中特列书神明于虚灵知觉之下。以此言之。又岂可以此二字。包得虚灵不昧而不别言之。以示夫知性穷理与不动心从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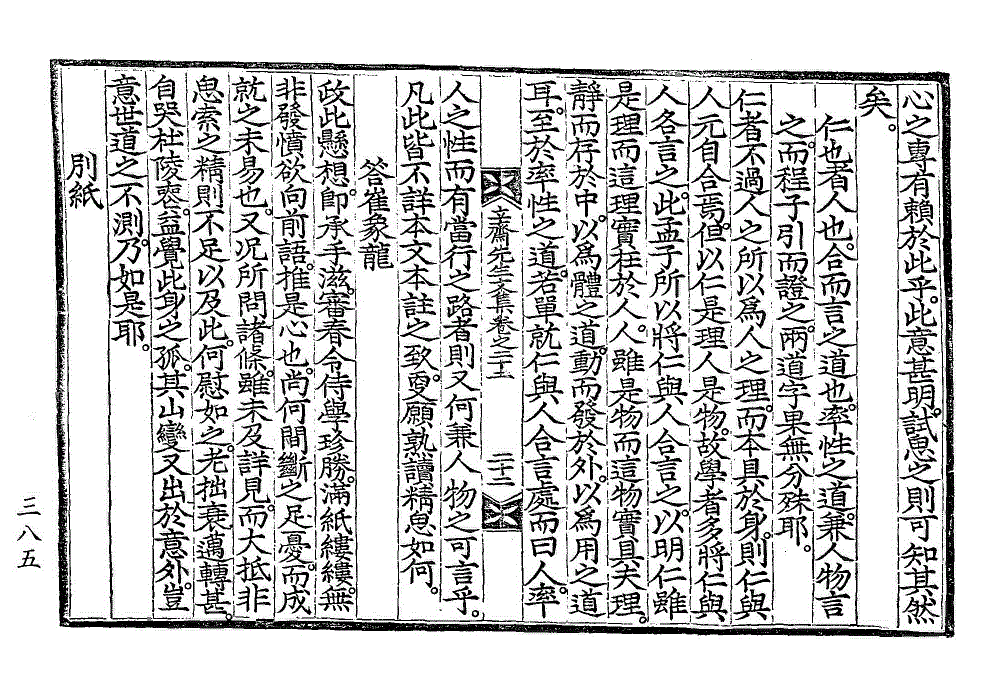 心之专有赖于此乎。此意甚明。试思之则可知其然矣。
心之专有赖于此乎。此意甚明。试思之则可知其然矣。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道。兼人物言之。而程子引而證之。两道字果无分殊耶。
仁者不过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而本具于身。则仁与人元自合焉。但以仁是理人是物。故学者多将仁与人各言之。此孟子所以将仁与人合言之。以明仁虽是理而这理实在于人。人虽是物而这物实具夫理。静而存于中。以为体之道。动而发于外。以为用之道耳。至于率性之道。若单就仁与人合言处而曰人。率人之性而有当行之路者则又何兼人物之可言乎。凡此皆不详本文本注之致。更愿熟读精思如何。
答崔象龙
政此悬想。即承手滋。审春令侍学珍胜。满纸缕缕。无非发愤欲向前语。推是心也。尚何间断之足忧。而成就之未易也。又况所问诸条。虽未及详见。而大抵非思索之精则不足以及此。何慰如之。老拙衰迈转甚。自哭杜陵丧。益觉此身之孤。其山变又出于意外。岂意世道之不测。乃如是耶。
别纸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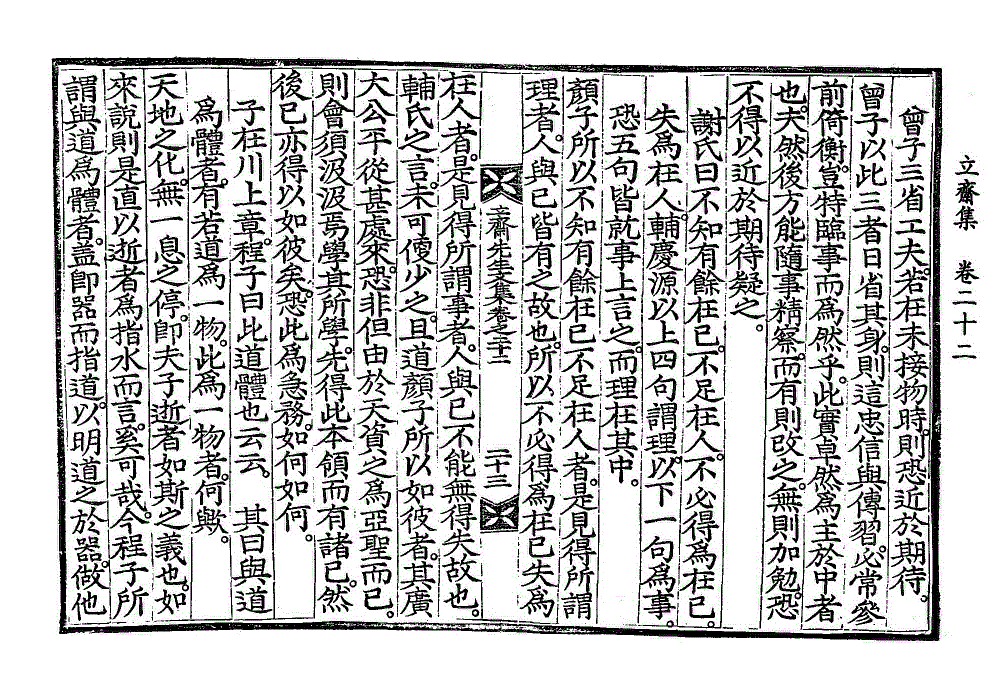 曾子三省工夫。若在未接物时。则恐近于期待。
曾子三省工夫。若在未接物时。则恐近于期待。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则这忠信与传习。必常参前倚衡。岂特临事而为然乎。此实卓然为主于中者也。夫然后方能随事精察。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恐不得以近于期待疑之。
谢氏曰不知有馀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辅庆源以上四句谓理。以下一句为事。恐五句皆就事上言之。而理在其中。
颜子所以不知有馀在己不足在人者。是见得所谓理者。人与己皆有之故也。所以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者。是见得所谓事者。人与己不能无得失故也。辅氏之言。未可便少之。且道颜子所以如彼者。其广大公平从甚处来。恐非但由于天资之为亚圣而已。则会须汲汲焉学其所学。先得此本领而有诸己。然后己亦得以如彼矣。恐此为急务。如何如何。
子在川上章。程子曰此道体也云云。 其曰与道为体者。有若道为一物。此为一物者。何欤。
天地之化。无一息之停。即夫子逝者如斯之义也。如来说则是直以逝者为指水而言。奚可哉。今程子所谓与道为体者。盖即器而指道。以明道之于器。做他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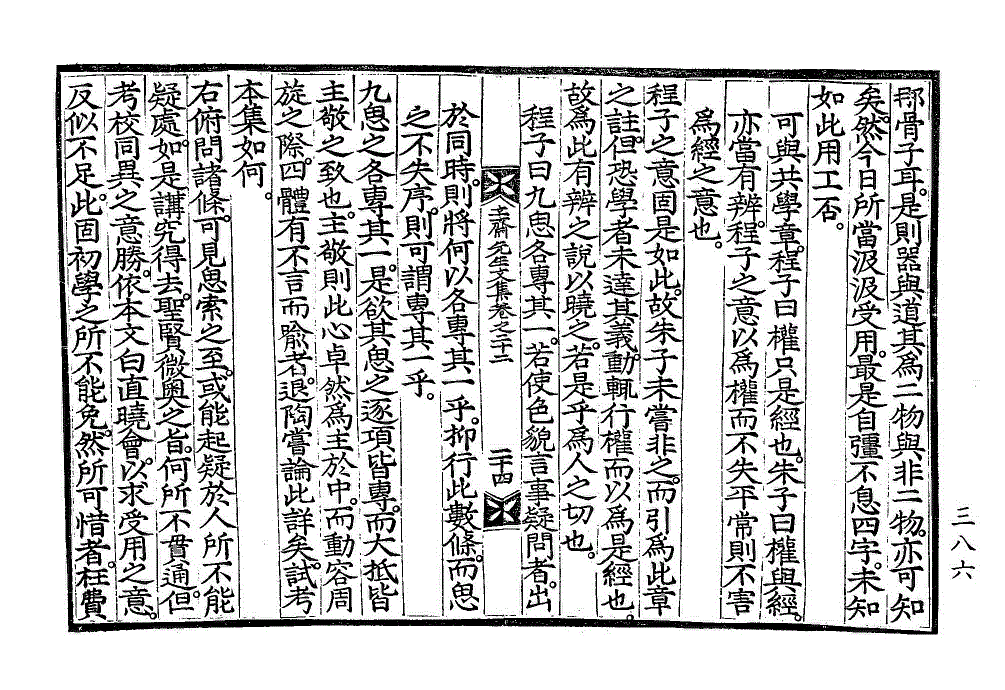 那骨子耳。是则器与道其为二物与非二物。亦可知矣。然今日所当汲汲受用。最是自彊不息四字。未知如此用工否。
那骨子耳。是则器与道其为二物与非二物。亦可知矣。然今日所当汲汲受用。最是自彊不息四字。未知如此用工否。可与共学章。程子曰权只是经也。朱子曰权与经。亦当有辨。程子之意以为权而不失平常则不害为经之意也。
程子之意固是如此。故朱子未尝非之。而引为此章之注。但恐学者未达其义。动辄行权而以为是经也。故为此有辨之说以晓之。若是乎为人之切也。
程子曰九思各专其一。若使色貌言事疑问者。出于同时。则将何以各专其一乎。抑行此数条。而思之不失序。则可谓专其一乎。
九思之各专其一。是欲其思之逐项皆专。而大抵皆主敬之致也。主敬则此心卓然为主于中。而动容周旋之际。四体有不言而喻者。退陶尝论此详矣。试考本集如何。
右俯问诸条。可见思索之至。或能起疑于人所不能疑处。如是讲究得去。圣贤微奥之旨。何所不贯通。但考校同异之意胜。依本文白直晓会。以求受用之意。反似不足。此固初学之所不能免。然所可惜者。枉费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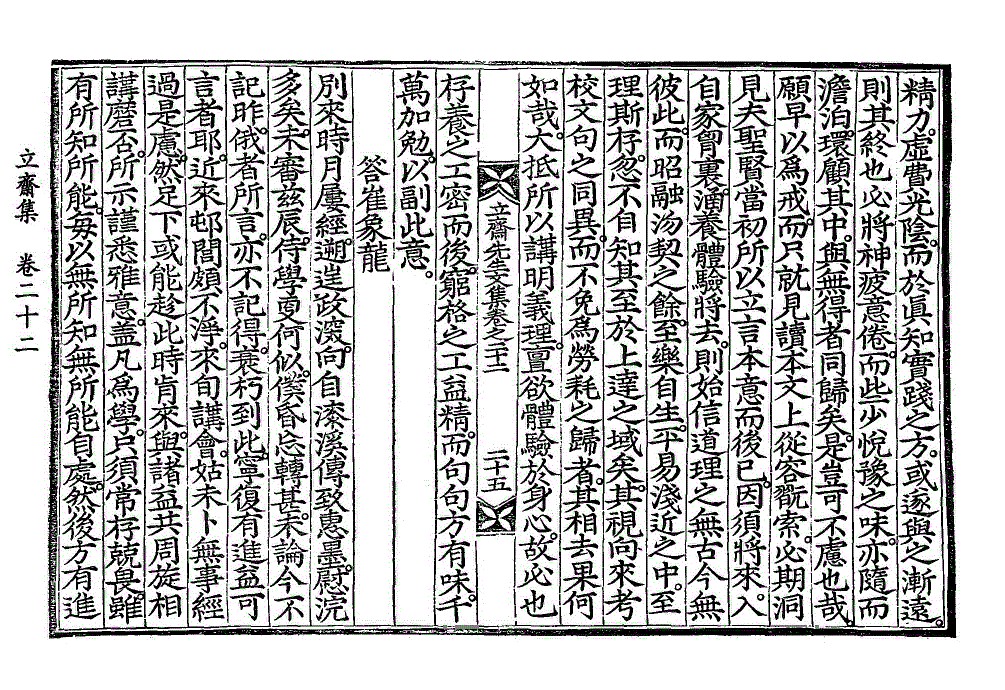 精力。虚费光阴。而于真知实践之方。或遂与之渐远。则其终也必将神疲意倦。而些少悦豫之味。亦随而澹泊。环顾其中。与无得者同归矣。是岂可不虑也哉。愿早以为戒。而只就见读本文上从容玩索。必期洞见夫圣贤当初所以立言本意而后已。因须将来。入自家胸里。涵养体验将去。则始信道理之无古今无彼此。而昭融吻契之馀。至乐自生。平易浅近之中。至理斯存。忽不自知其至于上达之域矣。其视向来考校文句之同异。而不免为劳耗之归者。其相去果何如哉。大抵所以讲明义理。亶欲体验于身心。故必也存养之工密而后。穷格之工益精。而句句方有味。千万加勉。以副此意。
精力。虚费光阴。而于真知实践之方。或遂与之渐远。则其终也必将神疲意倦。而些少悦豫之味。亦随而澹泊。环顾其中。与无得者同归矣。是岂可不虑也哉。愿早以为戒。而只就见读本文上从容玩索。必期洞见夫圣贤当初所以立言本意而后已。因须将来。入自家胸里。涵养体验将去。则始信道理之无古今无彼此。而昭融吻契之馀。至乐自生。平易浅近之中。至理斯存。忽不自知其至于上达之域矣。其视向来考校文句之同异。而不免为劳耗之归者。其相去果何如哉。大抵所以讲明义理。亶欲体验于身心。故必也存养之工密而后。穷格之工益精。而句句方有味。千万加勉。以副此意。答崔象龙
别来时月屡经。溯𨓏政深。向自漆溪传致惠墨。慰浣多矣。未审玆辰。侍学更何似。仆昏忘转甚。未论今不记昨。俄者所言。亦不记得。衰朽到此。宁复有进益可言者耶。近来村闾颇不净。来旬讲会。姑未卜无事经过是虑。然足下或能趁此时肯来。与诸益共周旋相讲磨否。所示谨悉雅意。盖凡为学。只须常存兢畏。虽有所知所能。每以无所知无所能自处。然后方有进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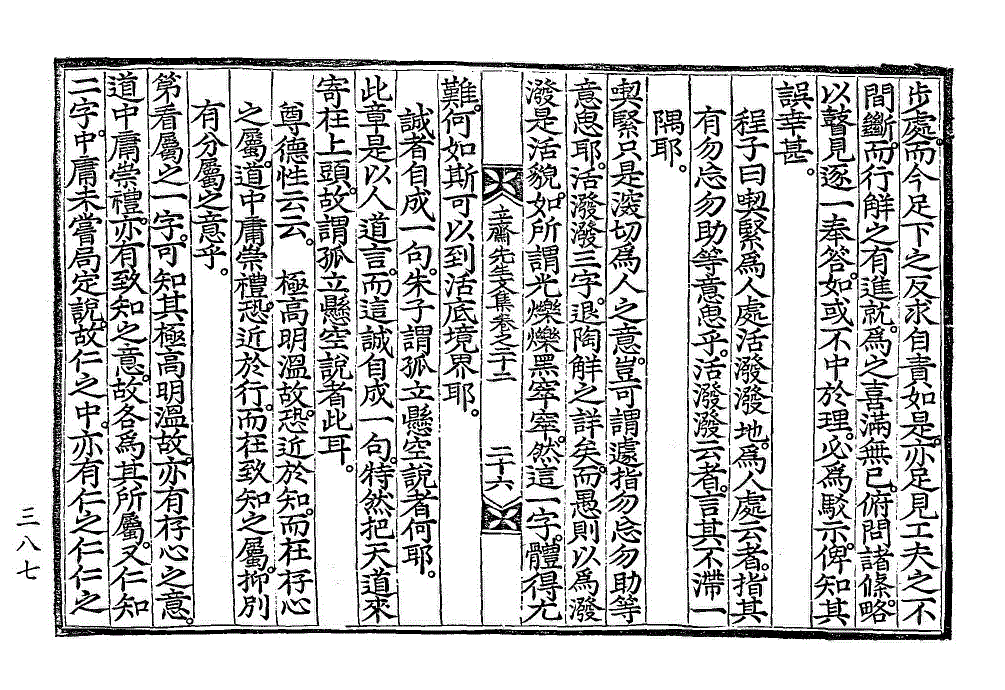 步处。而今足下之反求自责如是。亦足见工夫之不间断。而行解之有进就。为之喜满无已。俯问诸条。略以瞽见逐一奉答。如或不中于理。必为驳示。俾知其误幸甚。
步处。而今足下之反求自责如是。亦足见工夫之不间断。而行解之有进就。为之喜满无已。俯问诸条。略以瞽见逐一奉答。如或不中于理。必为驳示。俾知其误幸甚。程子曰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为人处云者。指其有勿忘勿助等意思乎。活泼泼云者。言其不滞一隅耶。
吃紧只是深切为人之意。岂可谓遽指勿忘勿助等意思耶。活泼泼三字。退陶解之详矣。而愚则以为泼泼是活貌。如所谓光烁烁黑窣窣。然这一字。体得尤难。何如斯可以到活底境界耶。
诚者自成一句。朱子谓孤立悬空说者何耶。
此章是以人道言。而这诚自成一句。特然把天道来寄在上头。故谓孤立悬空说者此耳。
尊德性云云。 极高明温故。恐近于知。而在存心之属。道中庸崇礼。恐近于行。而在致知之属。抑别有分属之意乎。
第看属之一字。可知其极高明温故。亦有存心之意。道中庸崇礼。亦有致知之意。故各为其所属。又仁知二字。中庸未尝局定说。故仁之中。亦有仁之仁仁之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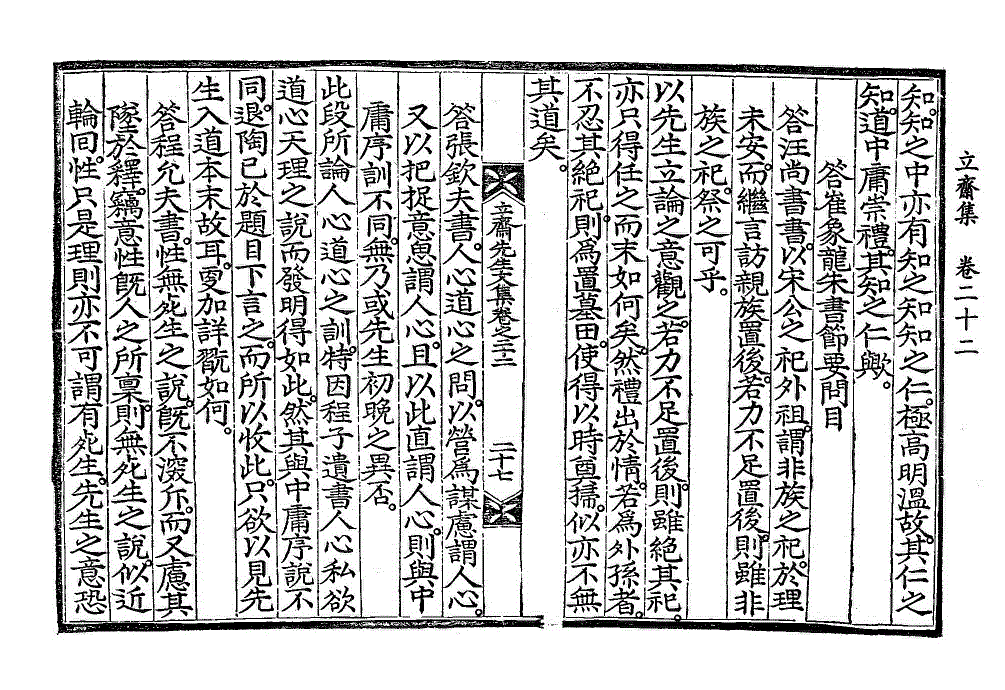 知。知之中亦有知之知知之仁。极高明温故。其仁之知。道中庸崇礼。其知之仁欤。
知。知之中亦有知之知知之仁。极高明温故。其仁之知。道中庸崇礼。其知之仁欤。答崔象龙朱书节要问目
答汪尚书书。以宋公之祀外祖。谓非族之祀。于理未安。而继言访亲族置后。若力不足置后。则虽非族之祀。祭之可乎。
以先生立论之意观之。若力不足置后。则虽绝其祀。亦只得任之而末如何矣。然礼出于情。若为外孙者。不忍其绝祀。则为置墓田。使得以时奠扫。似亦不无其道矣。
答张钦夫书。人心道心之问。以营为谋虑谓人心。又以把捉意思谓人心。且以此直谓人心。则与中庸序训不同。无乃或先生初晚之异否。
此段所论人心道心之训。特因程子遗书人心私欲道心天理之说而发明得如此。然其与中庸序说不同。退陶已于题目下言之。而所以收此。只欲以见先生入道本末故耳。更加详玩如何。
答程允夫书。性无死生之说。既不深斥。而又虑其坠于释。窃意性既人之所禀。则无死生之说。似近轮回。性只是理则亦不可谓有死生。先生之意恐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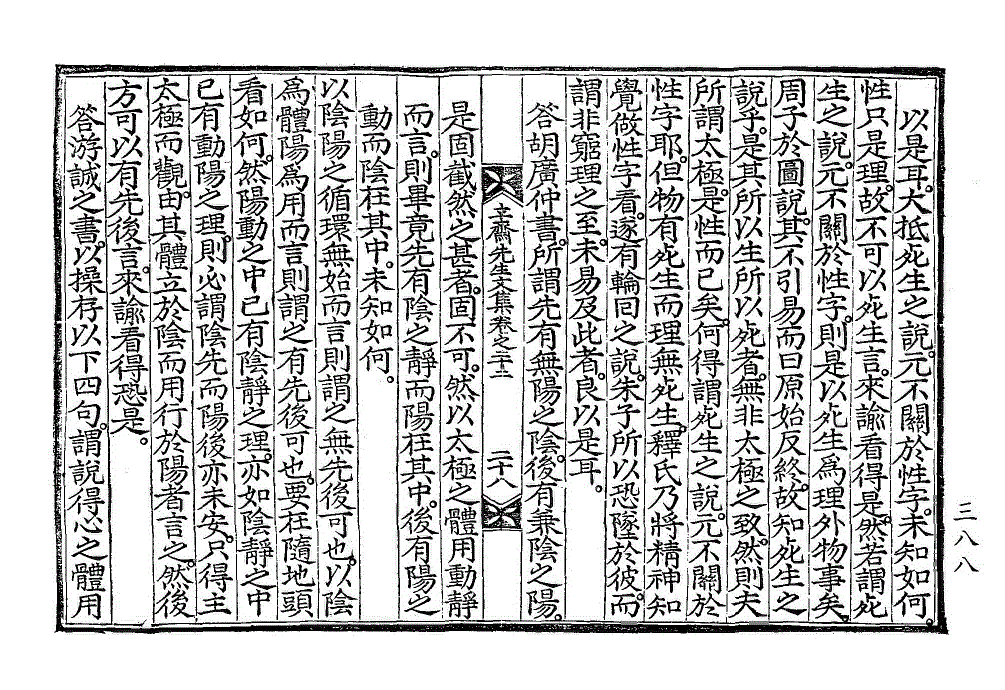 以是耳。大抵死生之说。元不关于性字。未知如何。
以是耳。大抵死生之说。元不关于性字。未知如何。性只是理。故不可以死生言。来谕看得是。然若谓死生之说。元不关于性字。则是以死生为理外物事矣。周子于图说。其不引易而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乎。是其所以生所以死者。无非太极之致。然则夫所谓太极。是性而已矣。何得谓死生之说。元不关于性字耶。但物有死生而理无死生。释氏乃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遂有轮回之说。朱子所以恐坠于彼。而谓非穷理之至。未易及此者。良以是耳。
答胡广仲书。所谓先有无阳之阴。后有兼阴之阳。是固截然之甚者。固不可。然以太极之体用动静而言。则毕竟先有阴之静而阳在其中。后有阳之动而阴在其中。未知如何。
以阴阳之循环无始而言则谓之无先后可也。以阴为体阳为用而言则谓之有先后可也。要在随地头看如何。然阳动之中已有阴静之理。亦如阴静之中已有动阳之理。则必谓阴先而阳后亦未安。只得主太极而观。由其体立于阴而用行于阳者言之。然后方可以有先后言。来谕看得恐是。
答游诚之书。以操存以下四句。谓说得心之体用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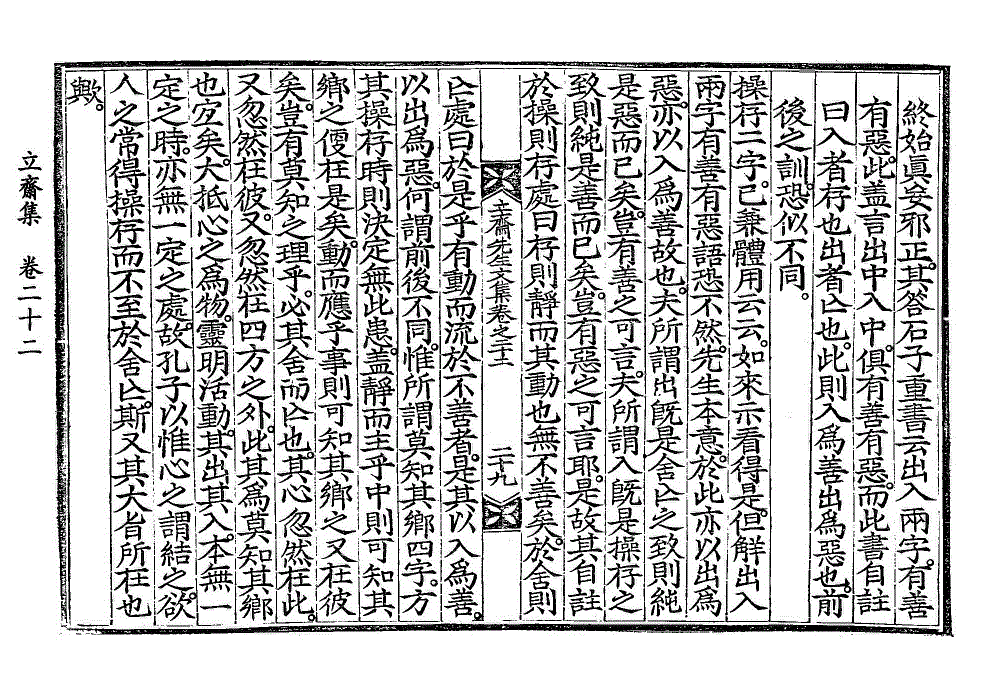 终始真妄邪正。其答石子重书云出入两字。有善有恶。此盖言出中入中。俱有善有恶。而此书自注曰入者存也出者亡也。此则入为善出为恶也。前后之训。恐似不同。
终始真妄邪正。其答石子重书云出入两字。有善有恶。此盖言出中入中。俱有善有恶。而此书自注曰入者存也出者亡也。此则入为善出为恶也。前后之训。恐似不同。操存二字。已兼体用云云。如来示看得是。但解出入两字有善有恶语恐不然。先生本意。于此亦以出为恶。亦以入为善故也。夫所谓出既是舍亡之致则纯是恶而已矣。岂有善之可言。夫所谓入既是操存之致则纯是善而已矣。岂有恶之可言耶。是故其自注于操则存处曰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矣。于舍则亡处曰于是乎有动而流于不善者。是其以入为善。以出为恶。何谓前后不同。惟所谓莫知其乡四字。方其操存时则决定无此患。盖静而主乎中则可知其乡之便在是矣。动而应乎事则可知其乡之又在彼矣。岂有莫知之理乎。必其舍而亡也。其心忽然在此。又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之外。此其为莫知其乡也宜矣。大抵心之为物。灵明活动。其出其入。本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故孔子以惟心之谓结之。欲人之常得操存而不至于舍亡。斯又其大旨所在也欤。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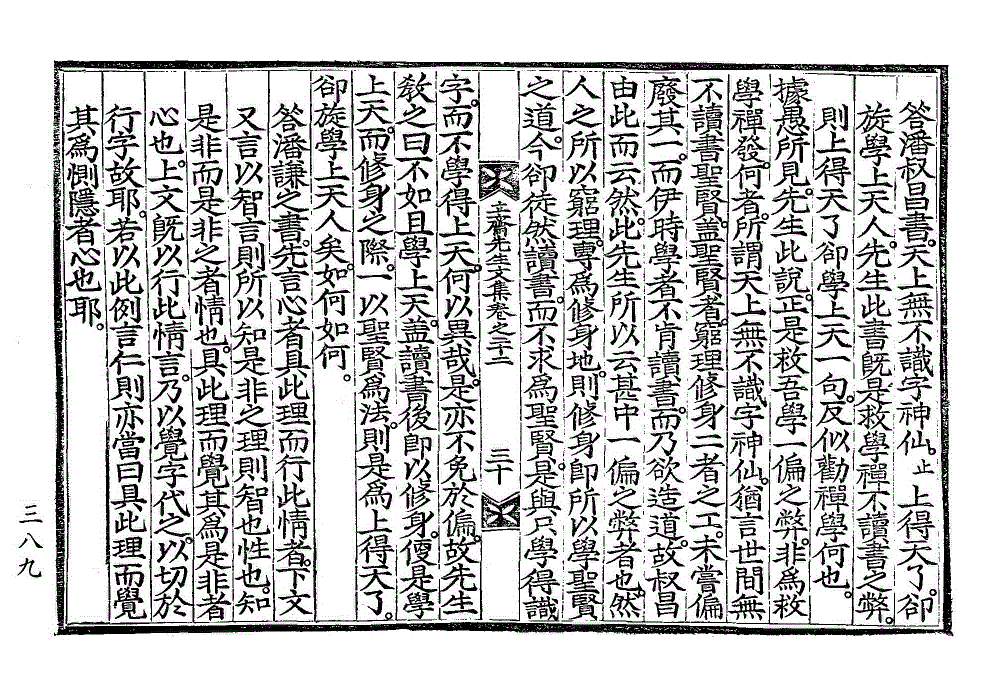 答潘叔昌书。天上无不识字神仙。(止)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先生此书既是救学禅不读书之弊。则上得天了却学上天一句。反似劝禅学何也。
答潘叔昌书。天上无不识字神仙。(止)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先生此书既是救学禅不读书之弊。则上得天了却学上天一句。反似劝禅学何也。据愚所见。先生此说。正是救吾学一偏之弊。非为救学禅发。何者。所谓天上无不识字神仙。犹言世间无不读书圣贤。盖圣贤者。穷理修身二者之工。未尝偏废其一。而伊时学者不肯读书。而乃欲造道。故叔昌由此而云然。此先生所以云甚中一偏之弊者也。然人之所以穷理。专为修身地。则修身即所以学圣贤之道。今却徒然读书。而不求为圣贤。是与只学得识字。而不学得上天。何以异哉。是亦不免于偏。故先生教之曰不如且学上天。盖读书后即以修身。便是学上天。而修身之际。一以圣贤为法。则是为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矣。如何如何。
答潘谦之书。先言心者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下文又言以智言则所以知是非之理则智也性也。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心也。上文既以行此情言。乃以觉字代之。以切于行字故耶。若以此例言仁则亦当曰具此理而觉其为恻隐者心也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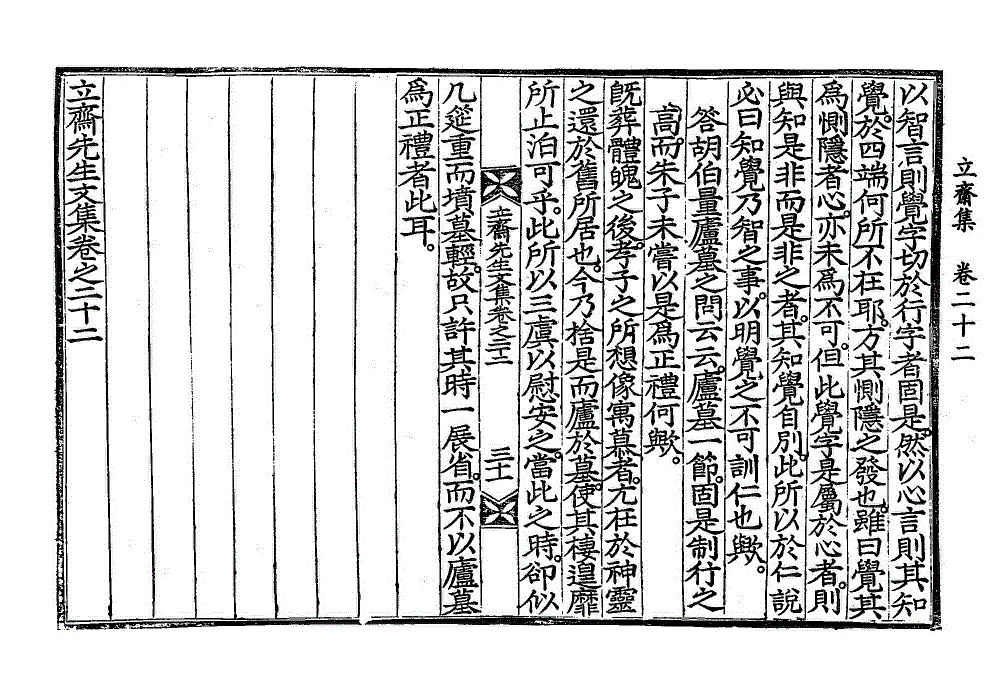 以智言则觉字切于行字者固是。然以心言则其知觉。于四端何所不在耶。方其恻隐之发也。虽曰觉其为恻隐者心。亦未为不可。但此觉字是属于心者。则与知是非而是非之者。其知觉自别。此所以于仁说必曰知觉乃智之事。以明觉之不可训仁也欤。
以智言则觉字切于行字者固是。然以心言则其知觉。于四端何所不在耶。方其恻隐之发也。虽曰觉其为恻隐者心。亦未为不可。但此觉字是属于心者。则与知是非而是非之者。其知觉自别。此所以于仁说必曰知觉乃智之事。以明觉之不可训仁也欤。答胡伯量庐墓之问云云。庐墓一节。固是制行之高。而朱子未尝以是为正礼何欤。
既葬体魄之后。孝子之所想像寓慕者。尤在于神灵之还于旧所居也。今乃舍是而庐于墓。使其栖遑靡所止泊可乎。此所以三虞以慰安之。当此之时。却似几筵重而坟墓轻。故只许其时一展省。而不以庐墓为正礼者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