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书
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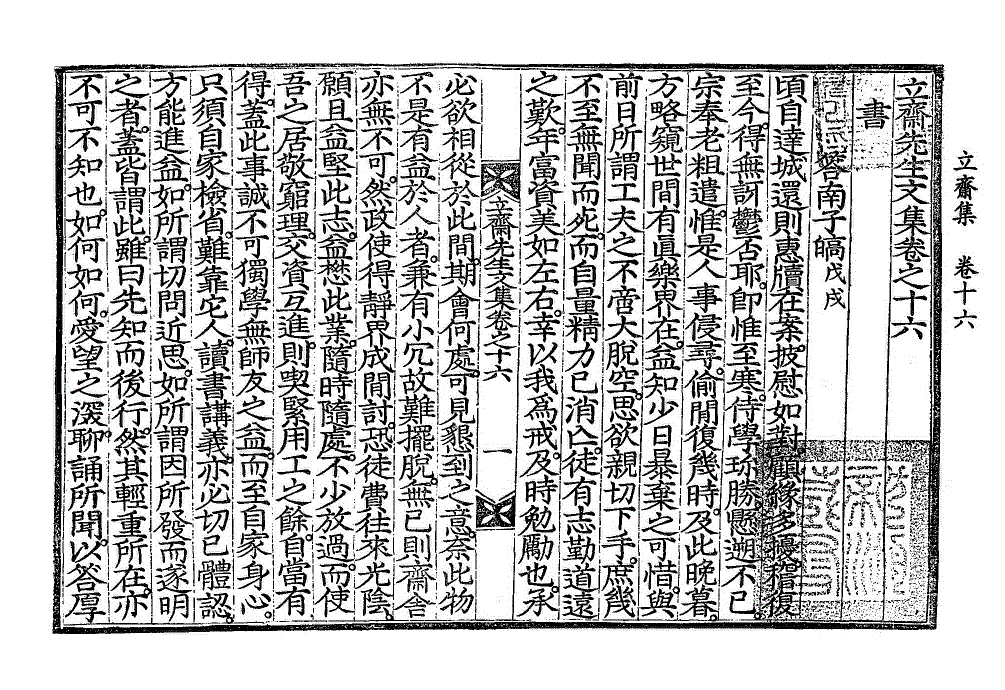 答南子皓(戊戌)
答南子皓(戊戌)顷自达城还则惠牍在案。披慰如对。顾缘多扰。稽复至今。得无讶郁否耶。即惟至寒。侍学珍胜。悬溯不已。宗奉老粗遣。惟是人事侵寻。偷閒复几时。及此晚暮。方略窥世间有真乐界在。益知少日暴弃之可惜。与前日所谓工夫之不啻大脱空。思欲亲切下手。庶几不至无闻而死。而自量精力已消亡。徒有志勤道远之叹。年富资美如左右。幸以我为戒。及时勉励也。承必欲相从于此间。期会何处。可见恳到之意。奈此物不是有益于人者。兼有小冗故难摆脱。无已则斋舍亦无不可。然政使得静界成閒讨。恐徒费往来光阴。愿且益坚此志。益懋此业。随时随处。不少放过。而使吾之居敬穷理。交资互进。则吃紧用工之馀。自当有得。盖此事诚不可独学无师友之益。而至自家身心。只须自家检省。难靠它人。读书讲义。亦必切己体认。方能进益。如所谓切问近思。如所谓因所发而遂明之者。盖皆谓此。虽曰先知而后行。然其轻重所在。亦不可不知也。如何如何。爱望之深。聊诵所闻。以答厚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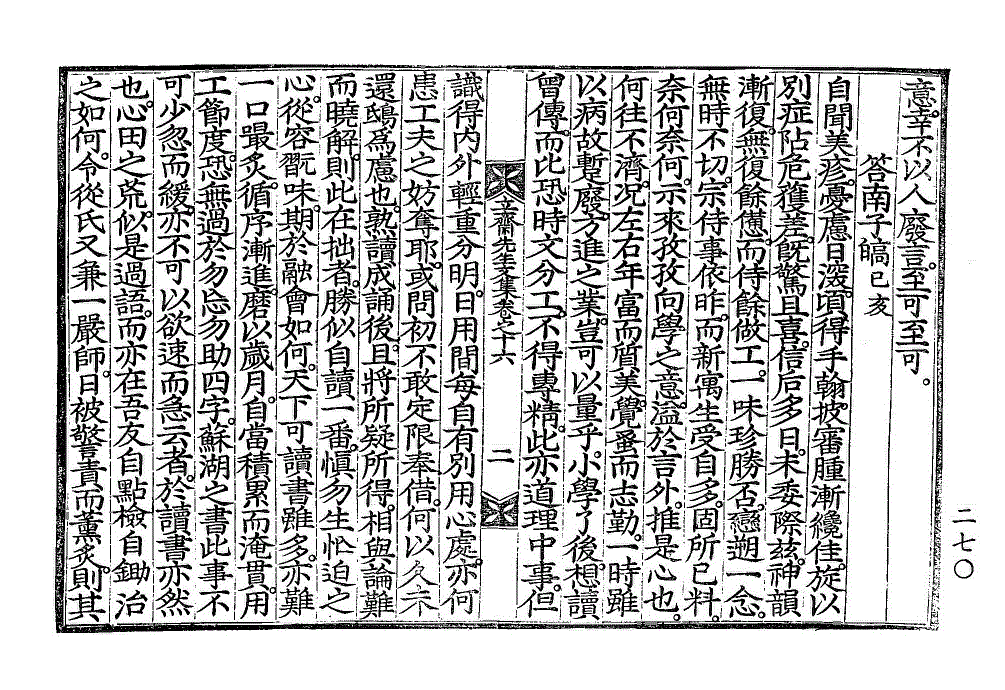 意。幸不以人废言。至可至可。
意。幸不以人废言。至可至可。答南子皓(己亥)
自闻美疹。忧虑日深。顷得手翰。披审肿渐才佳。旋以别症阽危获差。既惊且喜。信后多日。未委际玆。神韵渐复。无复馀惫。而侍馀做工。一味珍胜否。恋溯一念。无时不切。宗侍事依昨。而新寓生受自多。固所已料。奈何奈何。示来孜孜向学之意。溢于言外。推是心也。何往不济。况左右年富而质美。觉蚤而志勤。一时虽以病故暂废。方进之业。岂可以量乎。小学了后。想读曾传。而比恐时文分工。不得专精。此亦道理中事。但识得内外轻重分明。日用间每自有别用心处。亦何患工夫之妨夺耶。或问初不敢定限奉借。何以久未还鸱为虑也。熟读成诵后。且将所疑所得。相与论难而晓解。则此在拙者。胜似自读一番。慎勿生忙迫之心。从容玩味。期于融会如何。天下可读书虽多。亦难一口嘬炙。循序渐进。磨以岁月。自当积累而淹贯。用工节度。恐无过于勿忘勿助四字。苏湖之书此事不可少忽而缓。亦不可以欲速而急云者。于读书亦然也。心田之荒。似是过语。而亦在吾友自点检自锄治之如何。令从氏又兼一严师。日被警责而薰炙。则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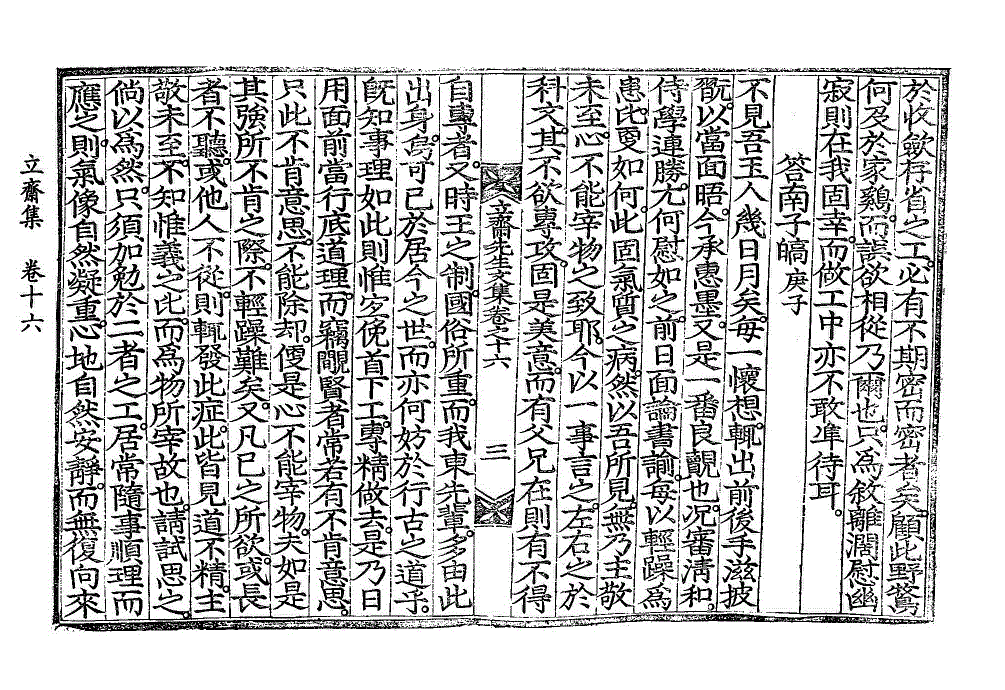 于收敛存省之工。必有不期密而密者矣。顾此野鹜何及于家鸡。而误欲相从乃尔也。只为叙离阔慰幽寂则在我固幸。而做工中亦不敢准待耳。
于收敛存省之工。必有不期密而密者矣。顾此野鹜何及于家鸡。而误欲相从乃尔也。只为叙离阔慰幽寂则在我固幸。而做工中亦不敢准待耳。答南子皓(庚子)
不见吾玉人几日月矣。每一怀想。辄出前后手滋披玩。以当面晤。今承惠墨。又是一番良觌也。况审清和。侍学连胜。尤何慰如之。前日面论书谕。每以轻躁为患。比更如何。此固气质之病。然以吾所见。无乃主敬未至。心不能宰物之致耶。今以一事言之。左右之于科文。其不欲专攻。固是美意。而有父兄在则有不得自专者。又时王之制。国俗所重。而我东先辈。多由此出身。乌可已于居今之世。而亦何妨于行古之道乎。既知事理如此则惟宜俛首下工。专精做去。是乃日用面前当行底道理。而窃覸贤者常若有不肯意思。只此不肯意思。不能除却。便是心不能宰物。夫如是其强所不肯之际。不轻躁难矣。又凡己之所欲。或长者不听。或他人不从。则辄发此症。此皆见道不精。主敬未至。不知惟义之比。而为物所宰故也。请试思之。倘以为然。只须加勉于二者之工。居常随事顺理而应之。则气像自然凝重。心地自然安静。而无复向来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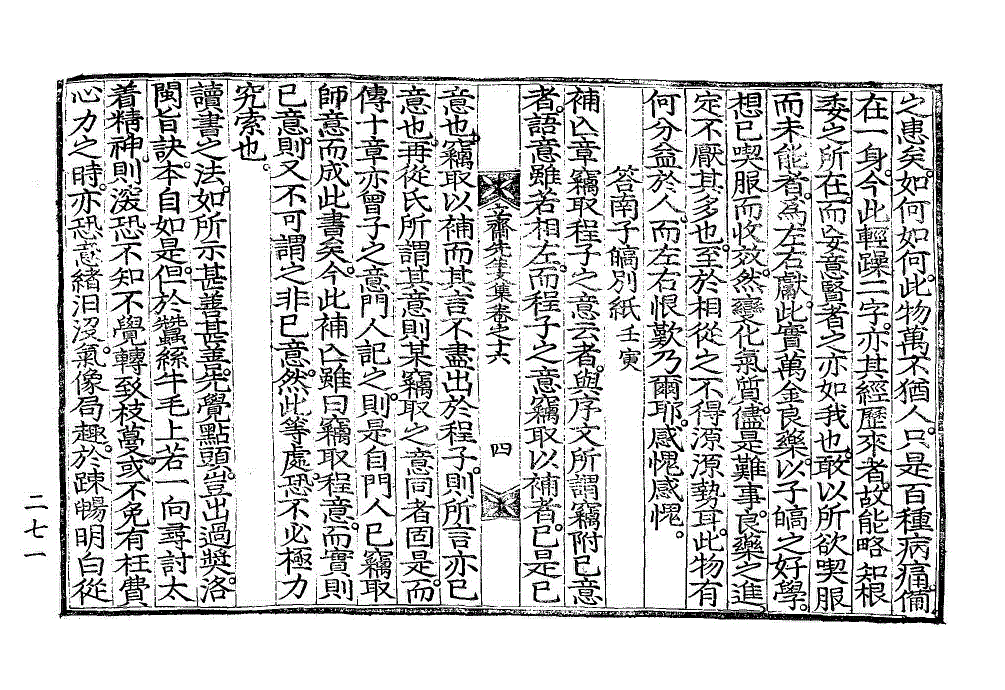 之患矣。如何如何。此物万不犹人。只是百种病痛。备在一身。今此轻躁二字。亦其经历来者。故能略知根委之所在。而妄意贤者之亦如我也。敢以所欲吃服而未能者。为左右献。此实万金良药。以子皓之好学。想已吃服而收效。然变化气质。尽是难事。良药之进。定不厌其多也。至于相从之不得源源势耳。此物有何分益于人。而左右恨叹乃尔耶。感愧感愧。
之患矣。如何如何。此物万不犹人。只是百种病痛。备在一身。今此轻躁二字。亦其经历来者。故能略知根委之所在。而妄意贤者之亦如我也。敢以所欲吃服而未能者。为左右献。此实万金良药。以子皓之好学。想已吃服而收效。然变化气质。尽是难事。良药之进。定不厌其多也。至于相从之不得源源势耳。此物有何分益于人。而左右恨叹乃尔耶。感愧感愧。答南子皓别纸(壬寅)
补亡章窃取程子之意云者。与序文所谓窃附己意者。语意虽若相左。而程子之意窃取以补者。已是己意也。窃取以补而其言不尽出于程子。则所言亦己意也。再从氏所谓其意则某窃取之意同者固是。而传十章亦曾子之意门人记之。则是自门人已窃取师意而成此书矣。今此补亡虽曰窃取程意。而实则己意。则又不可谓之非己意。然此等处。恐不必极力究索也。
读书之法。如所示甚善甚善。先觉点头。岂出过奖。洛闽旨诀。本自如是。但于蚕丝牛毛上若一向寻讨太着精神。则深恐不知不觉转致枝蔓。或不免有枉费心力之时。亦恐意绪汩没。气像局趣。于疏畅明白从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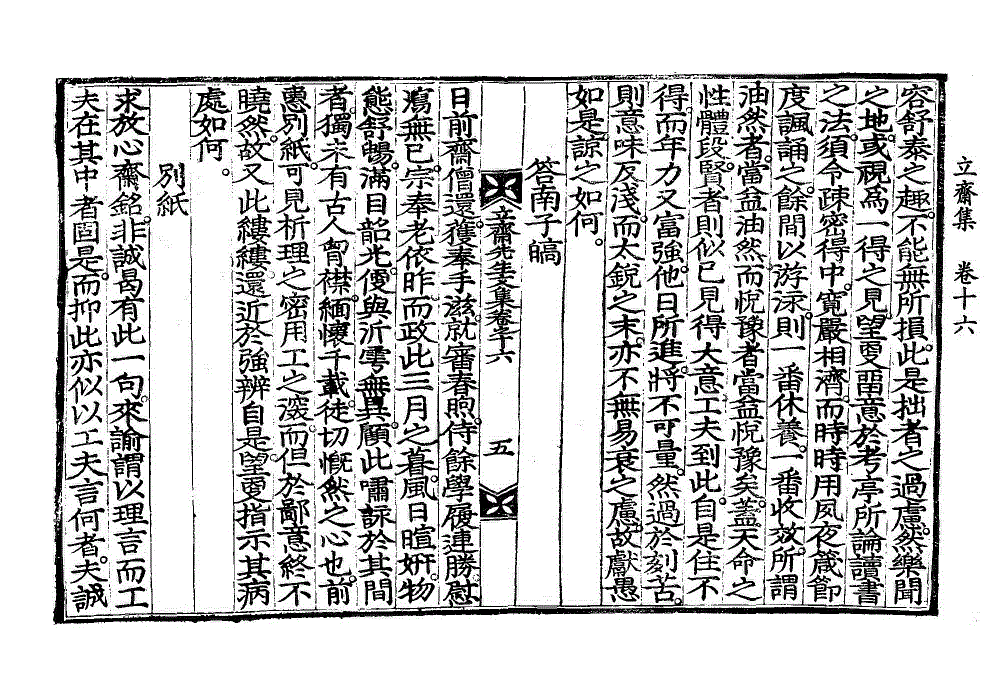 容舒泰之趣。不能无所损。此是拙者之过虑。然乐闻之地。或视为一得之见。望更留意于考亭所论读书之法。须令疏密得中。宽严相济。而时时用夙夜箴节度讽诵之。馀间以游泳。则一番休养。一番收效。所谓油然者。当益油然。而悦豫者当益悦豫矣。盖天命之性体段。贤者则似已见得大意。工夫到此。自是住不得。而年力又富强。他日所进。将不可量。然过于刻苦。则意味反浅。而太锐之末。亦不无易衰之虑。故献愚如是。谅之如何。
容舒泰之趣。不能无所损。此是拙者之过虑。然乐闻之地。或视为一得之见。望更留意于考亭所论读书之法。须令疏密得中。宽严相济。而时时用夙夜箴节度讽诵之。馀间以游泳。则一番休养。一番收效。所谓油然者。当益油然。而悦豫者当益悦豫矣。盖天命之性体段。贤者则似已见得大意。工夫到此。自是住不得。而年力又富强。他日所进。将不可量。然过于刻苦。则意味反浅。而太锐之末。亦不无易衰之虑。故献愚如是。谅之如何。答南子皓
日前斋僧还。获奉手滋。就审春煦。侍馀学履连胜。慰泻无已。宗奉老依昨。而政此三月之暮。风日暄妍。物态舒畅。满目韶光。便与沂雩无异。顾此啸咏于其间者。独未有古人胸襟。缅怀千载。徒切慨然之心也。前惠别纸。可见析理之密用工之深。而但于鄙意终不晓然。故又此缕缕。还近于强辨自是。望更指示其病处如何。
别纸
求放心斋铭。非诚曷有此一句。来谕谓以理言而工夫在其中者固是。而抑此亦似以工夫言何者。夫诚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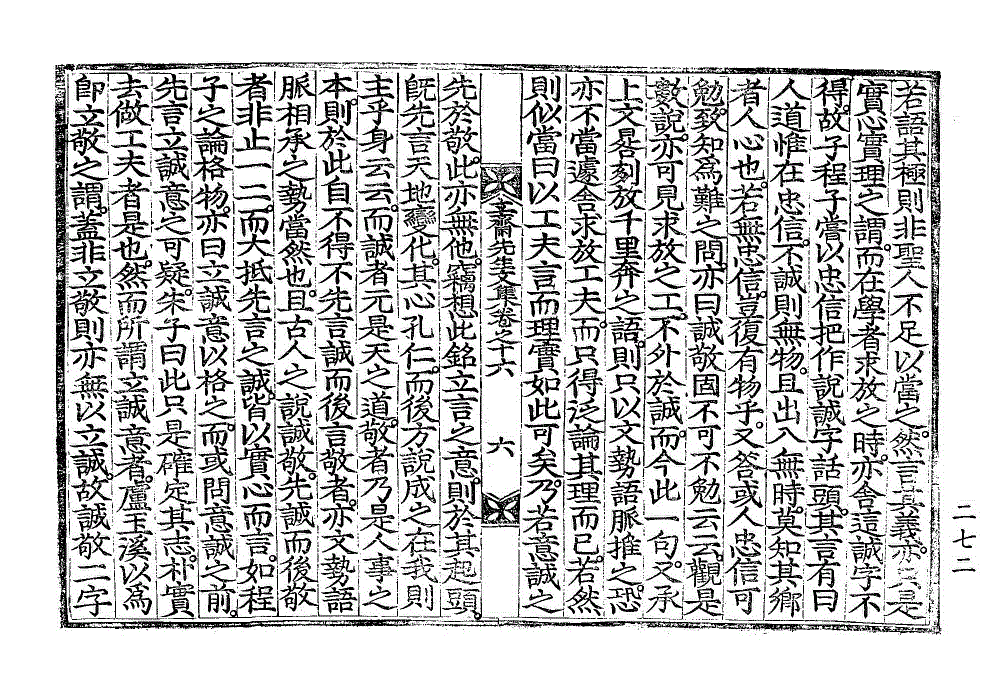 若语其极则非圣人不足以当之。然言其义。亦只是实心实理之谓。而在学者求放之时。亦舍这诚字不得。故子程子尝以忠信把作说诚字话头。其言有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又答或人忠信可勉。致知为难之问。亦曰诚敬固不可不勉云云。观是数说。亦可见求放之工。不外于诚。而今此一句。又承上文晷刻放千里奔之语。则只以文势语脉推之。恐亦不当遽舍求放工夫。而只得泛论其理而已。若然则似当曰以工夫言而理实如此可矣。乃若意诚之先于敬。此亦无他。窃想此铭立言之意。则于其起头。既先言天地变化。其心孔仁。而后方说成之在我则主乎身云云。而诚者元是天之道。敬者乃是人事之本。则于此自不得不先言诚而后言敬者。亦文势语脉相承之势当然也。且古人之说诚敬。先诚而后敬者非止一二。而大抵先言之诚。皆以实心而言。如程子之论格物。亦曰立诚意以格之。而或问意诚之前。先言立诚意之可疑。朱子曰此只是确定其志。朴实去做工夫者是也。然而所谓立诚意者。卢玉溪以为即立敬之谓。盖非立敬则亦无以立诚。故诚敬二字
若语其极则非圣人不足以当之。然言其义。亦只是实心实理之谓。而在学者求放之时。亦舍这诚字不得。故子程子尝以忠信把作说诚字话头。其言有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又答或人忠信可勉。致知为难之问。亦曰诚敬固不可不勉云云。观是数说。亦可见求放之工。不外于诚。而今此一句。又承上文晷刻放千里奔之语。则只以文势语脉推之。恐亦不当遽舍求放工夫。而只得泛论其理而已。若然则似当曰以工夫言而理实如此可矣。乃若意诚之先于敬。此亦无他。窃想此铭立言之意。则于其起头。既先言天地变化。其心孔仁。而后方说成之在我则主乎身云云。而诚者元是天之道。敬者乃是人事之本。则于此自不得不先言诚而后言敬者。亦文势语脉相承之势当然也。且古人之说诚敬。先诚而后敬者非止一二。而大抵先言之诚。皆以实心而言。如程子之论格物。亦曰立诚意以格之。而或问意诚之前。先言立诚意之可疑。朱子曰此只是确定其志。朴实去做工夫者是也。然而所谓立诚意者。卢玉溪以为即立敬之谓。盖非立敬则亦无以立诚。故诚敬二字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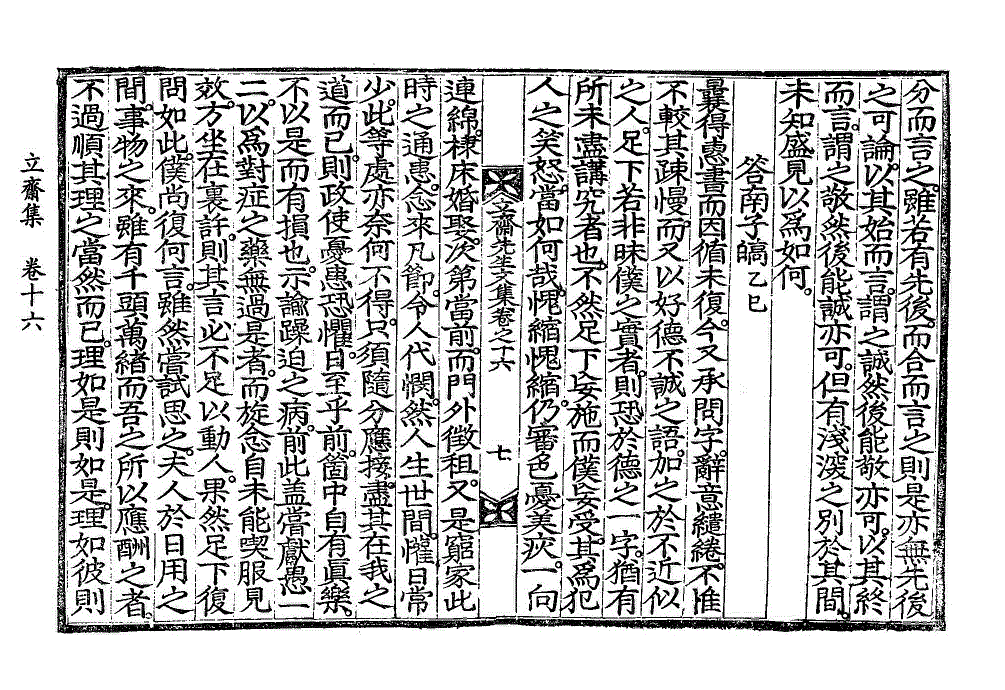 分而言之。虽若有先后。而合而言之则是亦无先后之可论。以其始而言。谓之诚然后能敬亦可。以其终而言。谓之敬然后能诚亦可。但有浅深之别于其间。未知盛见以为如何。
分而言之。虽若有先后。而合而言之则是亦无先后之可论。以其始而言。谓之诚然后能敬亦可。以其终而言。谓之敬然后能诚亦可。但有浅深之别于其间。未知盛见以为如何。答南子皓(乙巳)
曩得惠书而因循未复。今又承问字。辞意缱绻。不惟不较其疏慢。而又以好德不诚之语。加之于不近似之人。足下若非昧仆之实者。则恐于德之一字。犹有所未尽讲究者也。不然足下妄施而仆妄受。其为犯人之笑怒。当如何哉。愧缩愧缩。仍审色忧美疢。一向连绵。棣床婚娶。次第当前。而门外徵租。又是穷家此时之通患。念来凡节。令人代悯。然人生世间。欢日常少。此等处亦奈何不得。只须随分应接。尽其在我之道而已。则政使忧患恐惧。日至乎前。个中自有真乐。不以是而有损也。示谕躁迫之病。前此盖尝献愚一二。以为对症之药无过是者。而旋念自未能吃服见效。方坐在里许。则其言必不足以动人。果然足下复问如此。仆尚复何言。虽然尝试思之。夫人于日用之间。事物之来。虽有千头万绪。而吾之所以应酬之者。不过顺其理之当然而已。理如是则如是。理如彼则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3L 页
 如彼。一循其当然之则。而吾无所容心焉。尚何躁迫之足忧乎。此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者。苟非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地位。则固未易语此。然用工于穷理正心之学者。积习之久。自当如此。盖吾之于理。诚无所不明。而心体常虚。则凡遇事物之来。其先后缓急轻重疾徐之分。莫不灿然于鉴空衡平之中。照管称量。惟其所宜。而自无纷扰杂乱之患。及其应之也。又常从容而舒泰。虽或有左右交酬时节。极忙之处。自外观之。固不免动作之频繁。而其中之安閒。当自如也。吾与足下。何修而得到此地位耶。仆则已矣。愿以是为足下勉。幸望勿以人废言如何。
如彼。一循其当然之则。而吾无所容心焉。尚何躁迫之足忧乎。此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者。苟非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地位。则固未易语此。然用工于穷理正心之学者。积习之久。自当如此。盖吾之于理。诚无所不明。而心体常虚。则凡遇事物之来。其先后缓急轻重疾徐之分。莫不灿然于鉴空衡平之中。照管称量。惟其所宜。而自无纷扰杂乱之患。及其应之也。又常从容而舒泰。虽或有左右交酬时节。极忙之处。自外观之。固不免动作之频繁。而其中之安閒。当自如也。吾与足下。何修而得到此地位耶。仆则已矣。愿以是为足下勉。幸望勿以人废言如何。与南子皓(庚戌)
向得足下书。慰浣之心。迨犹未已。即日寒令。谨问侍馀学履。果甚似。仆近来摧颓益甚。体死用乱。作一无形之人久矣。今得再从氏箴砭之语。不觉惕然而有警发者存焉。夫以子夏之贤而离群索居。犹不免于有过。则如仆之愚。长此岑寂。又安得不如是耶。昏弱之质。善于流循。苟无畏友彊辅寻常忌惮之人。为之朝夕规诲。则不知不觉地。遂到于难收拾之境。所谓检身不足而酬世有馀。务积则蔑而受用是事者。真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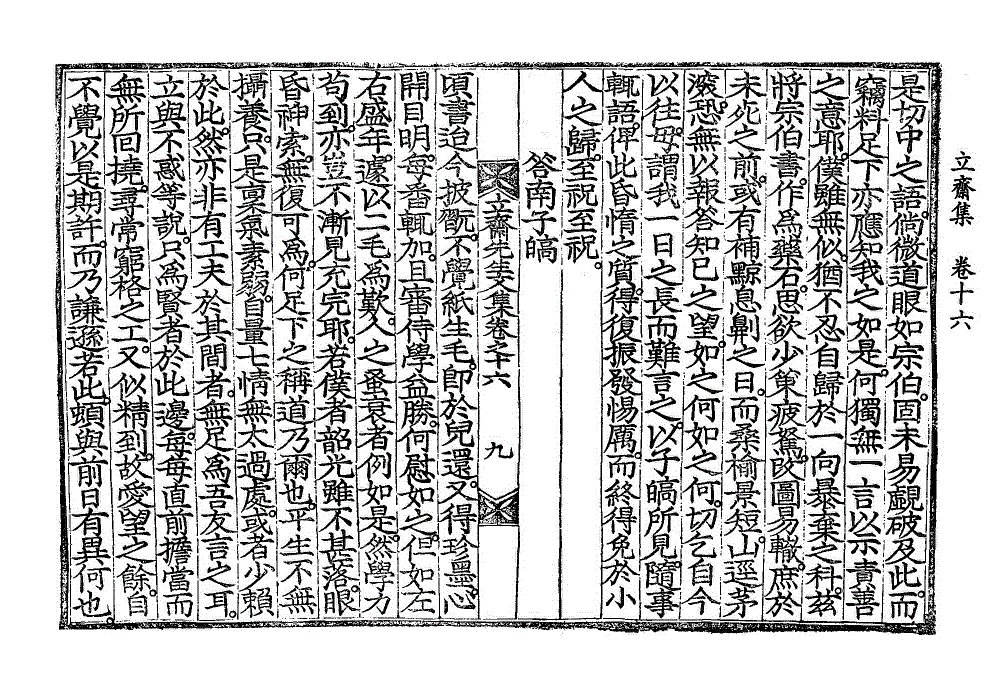 是切中之语。倘微道眼如宗伯。固未易觑破及此。而窃料足下亦应知我之如是。何独无一言以示责善之意耶。仆虽无似。犹不忍自归于一向暴弃之科。玆将宗伯书。作为药石。思欲少策疲驽。改图易辙。庶于未死之前。或有补黥息劓之日。而桑榆景短。山径茅深。恐无以报答知己之望。如之何如之何。切乞自今以往。毋谓我一日之长而难言之。以子皓所见。随事辄语。俾此昏惰之质。得复振发惕厉。而终得免于小人之归。至祝至祝。
是切中之语。倘微道眼如宗伯。固未易觑破及此。而窃料足下亦应知我之如是。何独无一言以示责善之意耶。仆虽无似。犹不忍自归于一向暴弃之科。玆将宗伯书。作为药石。思欲少策疲驽。改图易辙。庶于未死之前。或有补黥息劓之日。而桑榆景短。山径茅深。恐无以报答知己之望。如之何如之何。切乞自今以往。毋谓我一日之长而难言之。以子皓所见。随事辄语。俾此昏惰之质。得复振发惕厉。而终得免于小人之归。至祝至祝。答南子皓
顷书迨今披玩。不觉纸生毛。即于儿还。又得珍墨。心开目明。每番辄加。且审侍学益胜。何慰如之。但如左右盛年。遽以二毛为叹。人之蚤衰者例如是。然学力苟到。亦岂不渐见充完耶。若仆者韶光虽不甚落。眼昏神索。无复可为。何足下之称道乃尔也。平生不无摄养。只是禀气素弱。自量七情无太过处。或者少赖于此。然亦非有工夫于其间者。无足为吾友言之耳。立与不惑等说。只为贤者于此边。每每直前担当而无所回挠。寻常穷格之工。又似精到。故爱望之馀。自不觉以是期许。而乃谦逊若此。顿与前日有异何也。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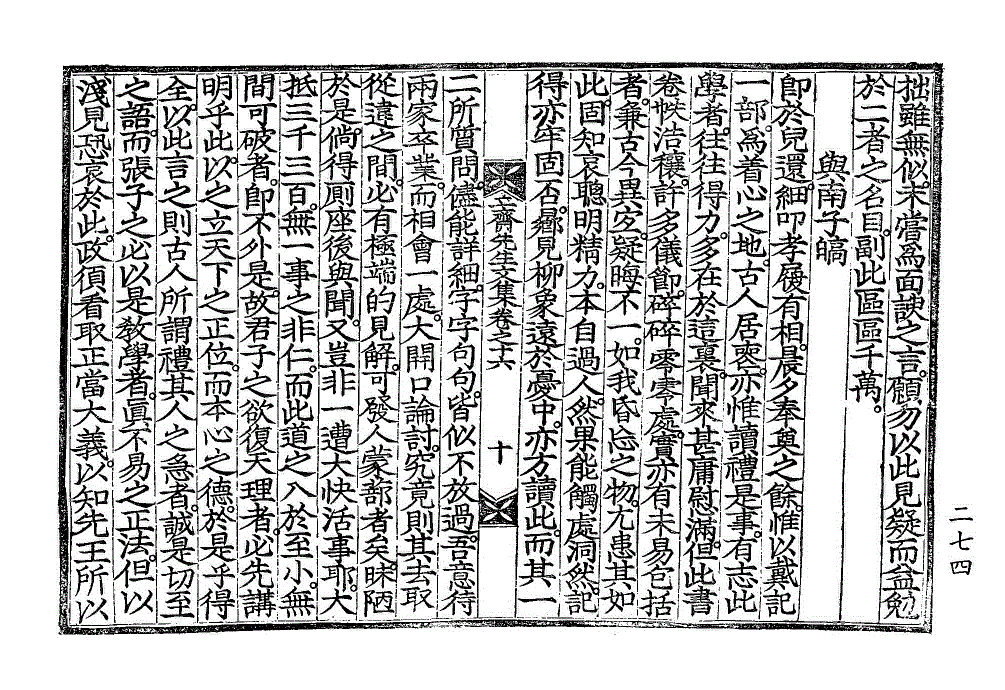 拙虽无似。未尝为面谀之言。愿勿以此见疑而益勉于二者之名目。副此区区千万。
拙虽无似。未尝为面谀之言。愿勿以此见疑而益勉于二者之名目。副此区区千万。与南子皓
即于儿还。细叩孝履有相。晨夕奉奠之馀。惟以戴记一部。为着心之地。古人居丧。亦惟读礼是事。有志此学者。往往得力。多在于这里。闻来甚庸慰满。但此书卷帙浩穰。许多仪节。碎碎零零处。实亦有未易包括者。兼古今异宜。疑晦不一。如我昏忘之物。尤患其如此。固知哀聪明精力。本自过人。然果能触处洞然。记得亦牢固否。向见柳象远于忧中。亦方读此。而其一二所质问。尽能详细。字字句句。皆似不放过。吾意待两家卒业。而相会一处。大开口论讨。究竟则其去取从违之间。必有极端的见解。可发人蒙蔀者矣。昧陋于是。倘得厕座后与闻。又岂非一遭大快活事耶。大抵三千三百。无一事之非仁。而此道之入于至小。无间可破者。即不外是。故君子之欲复天理者。必先讲明乎此。以之立天下之正位。而本心之德。于是乎得全。以此言之则古人所谓礼其人之急者。诚是切至之语。而张子之必以是教学者。真不易之正法。但以浅见恐哀于此。政须看取正当大义。以知先王所以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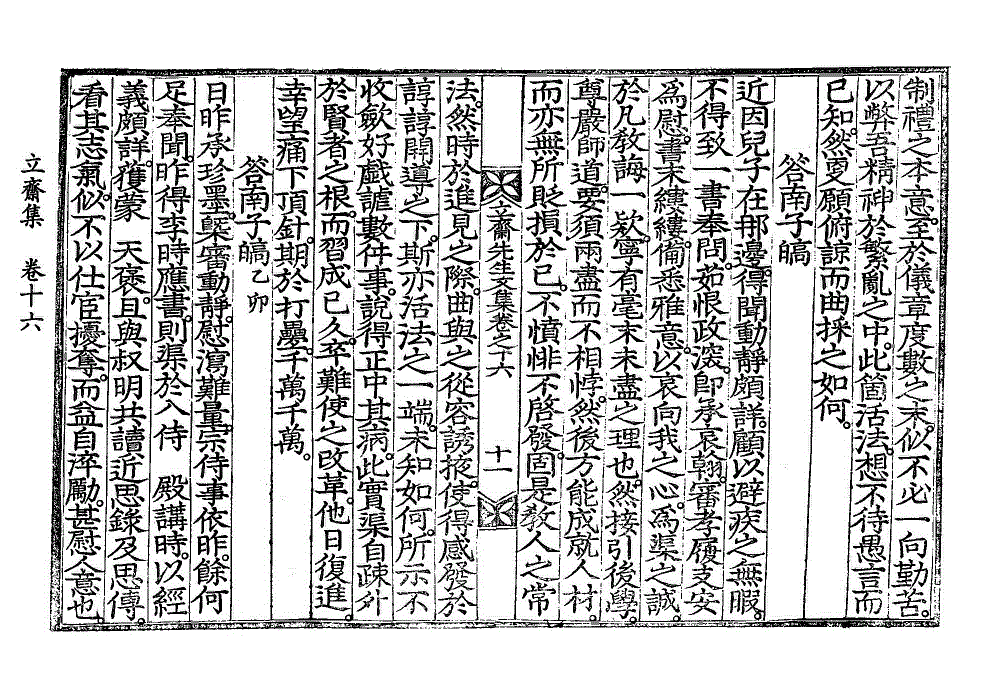 制礼之本意。至于仪章度数之末。似不必一向勤苦。以弊吾精神于繁乱之中。此个活法。想不待愚言而已知。然更愿俯谅而曲采之如何。
制礼之本意。至于仪章度数之末。似不必一向勤苦。以弊吾精神于繁乱之中。此个活法。想不待愚言而已知。然更愿俯谅而曲采之如何。答南子皓
近因儿子在那边。得闻动静颇详。顾以避疾之无暇。不得致一书奉问。茹恨政深。即承哀翰。审孝履支安为慰。书末缕缕。备悉雅意。以哀向我之心。为渠之诚。于凡教诲一款。宁有毫末未尽之理也。然接引后学。尊严师道。要须两尽而不相悖。然后方能成就人材。而亦无所贬损于己。不愤悱不启发。固是教人之常法。然时于进见之际。曲与之从容诱掖。使得感发于谆谆开导之下。斯亦活法之一端。未知如何。所示不收敛好戏谑数件事。说得正中其病。此实渠自疏外于贤者之根。而习成已久。卒难使之改革。他日复进。幸望痛下顶针。期于打叠。千万千万。
答南子皓(乙卯)
日昨承珍墨。槩审动静。慰泻难量。宗侍事依昨。馀何足奉闻。昨得李时应书。则渠于入侍 殿讲时。以经义颇详。获蒙 天褒。且与叔明共读近思录及思传。看其志气。似不以仕宦扰夺。而益自淬励。甚慰人意也。
与南子皓(丙辰)
别来已久。即玆花煦。侍馀学履如何。宗顷于乡饮时。猥当宾席。而胶扰中末由整顿仪节。只从一处所写笏记而行之。故其间不无零琐谬误之端。如使左右来相。则岂有此患。尚赖柳敬甫从傍提醒于前夕。为益不少。终是礼席上生疏者多。而閒习者少。又缘唱礼急遽呼之。使不得从容尽其节次。旷百年未举之盛礼。幸而得行于今日。而犹复如此者。诚可恨恨。然却念自家见解。未能分晓。致得扰夺于忙乱中。是愧如何。
答南子皓
比来音问更阻。即玆阴雨。侍馀学履如何。宗亲候幸免外添耳。辞职一款。以此悚怀之心。如遇更疏之端。岂容复为延稽。而向也始见李贞运应 旨疏。则以为虚縻台衔。不如趣召以备咨问。因授中外合试之职云。举论如彼则在我似不容泯默。故初欲因此为陈章之举。而旋念自 上若采用其言。似当于蚤晏间必有 处分。而于时沥恳未晚。遂不果焉。到今思之。却甚可悔。吾侪诸论。皆以为虽十疏期于必递。然后方无未安于心。盖以屡渎之未安少。虚带之未安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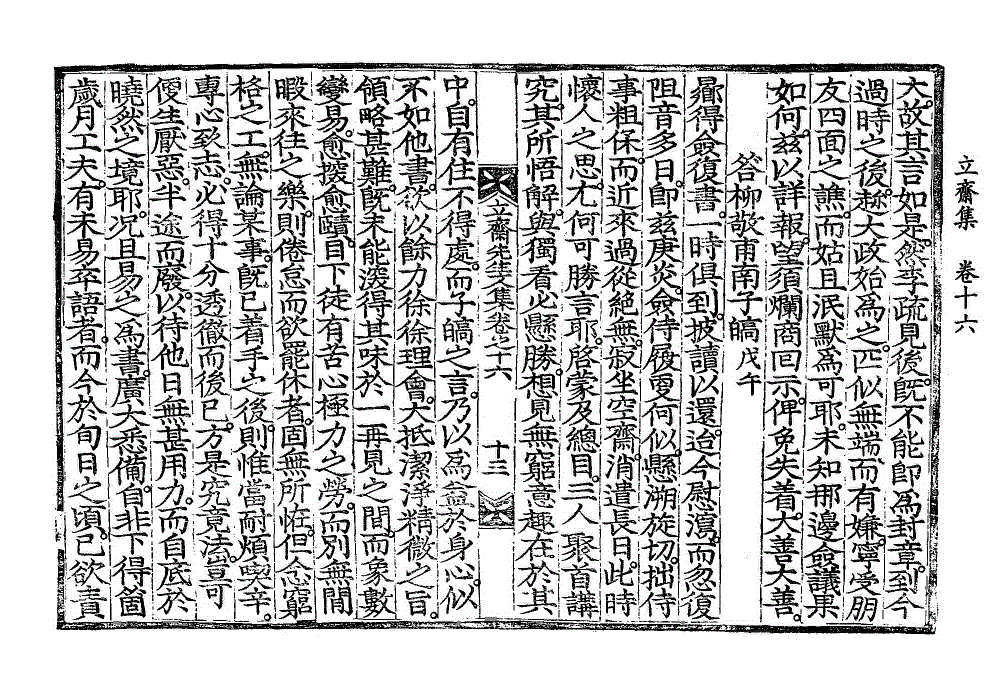 大。故其言如是。然李疏见后。既不能即为封章。到今过时之后。趁大政始为之。匹似无端而有嫌。宁受朋友四面之谯。而姑且泯默为可耶。未知那边佥议果如何。玆以详报。望须烂商回示。俾免失着。大善大善。
大。故其言如是。然李疏见后。既不能即为封章。到今过时之后。趁大政始为之。匹似无端而有嫌。宁受朋友四面之谯。而姑且泯默为可耶。未知那边佥议果如何。玆以详报。望须烂商回示。俾免失着。大善大善。答柳敬甫南子皓(戊午)
向得佥复书。一时俱到。披读以还。迨今慰泻。而忽复阻音多日。即玆庚炎。佥侍履更何似。悬溯旋切。拙侍事粗保。而近来过从绝无。寂坐空斋。消遣长日。此时怀人之思。尤何可胜言耶。启蒙及总目。三人聚首讲究。其所悟解。与独看必悬胜。想见无穷意趣在于其中。自有住不得处。而子皓之言。乃以为益于身心。似不如他书。欲以馀力徐徐理会。大抵洁净精微之旨。领略甚难。既未能深得其味于一再见之间。而象数变易。愈探愈赜。目下徒有苦心极力之劳。而别无閒暇来往之乐。则倦怠而欲罢休者。固无所怪。但念穷格之工。无论某事。既已着手之后。则惟当耐烦吃辛。专心致志。必得十分透彻而后已。方是究竟法。岂可便生厌恶。半途而废。以待他日无甚用力。而自底于晓然之境耶。况且易之为书。广大悉备。自非下得个岁月工夫。有未易卒语者。而今于旬日之顷。已欲责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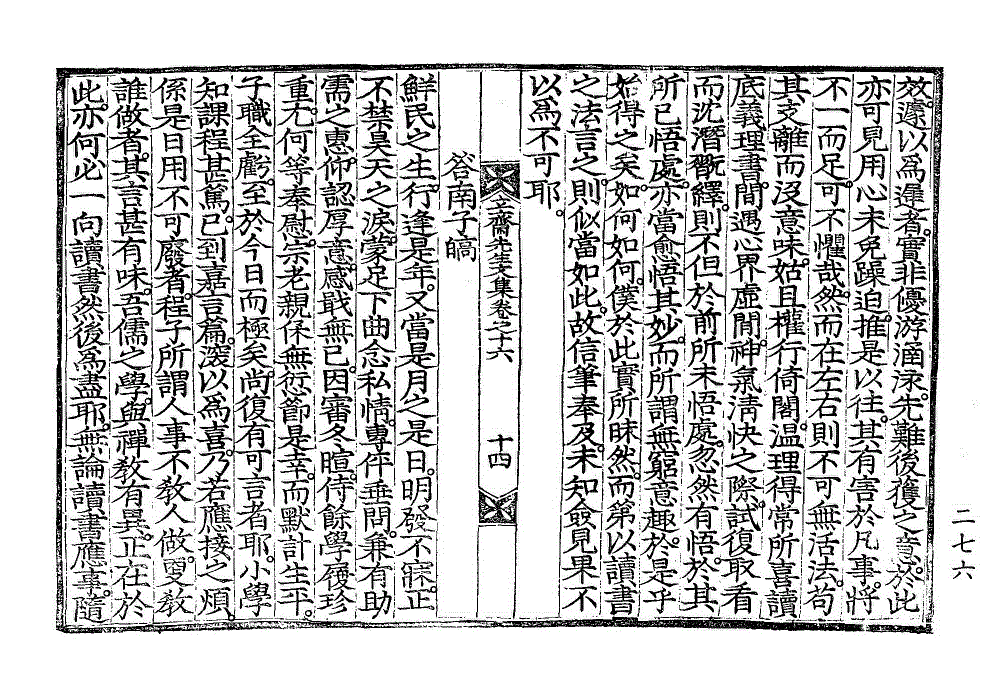 效。遽以为迟者。实非优游涵泳。先难后获之意。于此亦可见用心未免躁迫。推是以往。其有害于凡事。将不一而足。可不惧哉。然而在左右则不可无活法。苟其支离而没意味。姑且权行倚阁。温理得常所喜读底义理书。间遇心界虚閒。神气清快之际。试复取看而沈潜玩绎。则不但于前所未悟处。忽然有悟。于其所已悟处。亦当愈悟其妙。而所谓无穷意趣。于是乎始得之矣。如何如何。仆于此实所昧然。而第以读书之法言之。则似当如此。故信笔奉及。未知佥见果不以为不可耶。
效。遽以为迟者。实非优游涵泳。先难后获之意。于此亦可见用心未免躁迫。推是以往。其有害于凡事。将不一而足。可不惧哉。然而在左右则不可无活法。苟其支离而没意味。姑且权行倚阁。温理得常所喜读底义理书。间遇心界虚閒。神气清快之际。试复取看而沈潜玩绎。则不但于前所未悟处。忽然有悟。于其所已悟处。亦当愈悟其妙。而所谓无穷意趣。于是乎始得之矣。如何如何。仆于此实所昧然。而第以读书之法言之。则似当如此。故信笔奉及。未知佥见果不以为不可耶。答南子皓
鲜民之生。行逢是年。又当是月之是日。明发不寐。正不禁昊天之泪。蒙足下曲念私情。专伻垂问。兼有助需之惠。仰认厚意。感戢无已。因审冬暄。侍馀学履珍重。尤何等奉慰。宗老亲保无愆节是幸。而默计生平。子职全亏。至于今日而极矣。尚复有可言者耶。小学知课程甚笃。已到嘉言篇。深以为喜。乃若应接之烦。系是日用不可废者。程子所谓人事不教人做。更教谁做者。其言甚有味。吾儒之学。与禅教有异。正在于此。亦何必一向读书然后为尽耶。无论读书应事。随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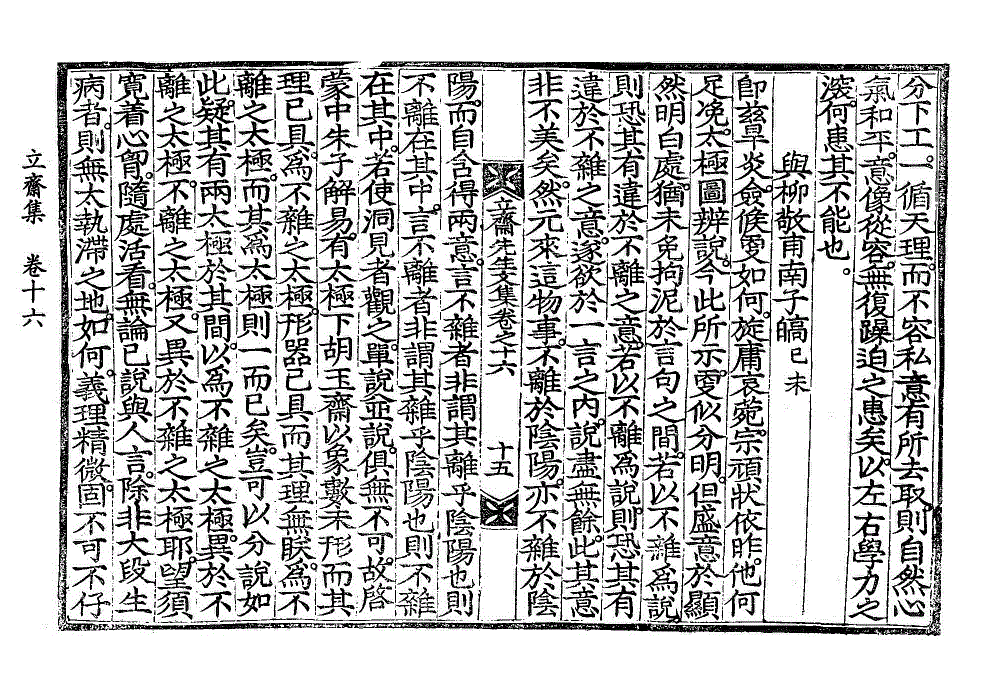 分下工。一循天理。而不容私意有所去取。则自然心气和平。意像从容。无复躁迫之患矣。以左右学力之深。何患其不能也。
分下工。一循天理。而不容私意有所去取。则自然心气和平。意像从容。无复躁迫之患矣。以左右学力之深。何患其不能也。与柳敬甫南子皓(己未)
即玆旱炎。佥候更如何。旋庸哀菀。宗顽状依昨。他何足浼。太极图辨说。今此所示。更似分明。但盛意于显然明白处。犹未免拘泥于言句之间。若以不杂为说。则恐其有违于不离之意。若以不离为说。则恐其有违于不杂之意。遂欲于一言之内。说尽无馀。此其意非不美矣。然元来这物事。不离于阴阳。亦不杂于阴阳。而自含得两意。言不杂者非谓其离乎阴阳也则不离在其中。言不离者非谓其杂乎阴阳也则不杂在其中。若使洞见者观之。单说并说。俱无不可。故启蒙中朱子解易。有太极下胡玉斋以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为不杂之太极。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为不离之太极。而其为太极则一而已矣。岂可以分说如此。疑其有两太极于其间。以为不杂之太极。异于不离之太极。不离之太极。又异于不杂之太极耶。望须宽着心胸。随处活看。无论己说与人言。除非大段生病者。则无太执滞之地。如何。义理精微。固不可不仔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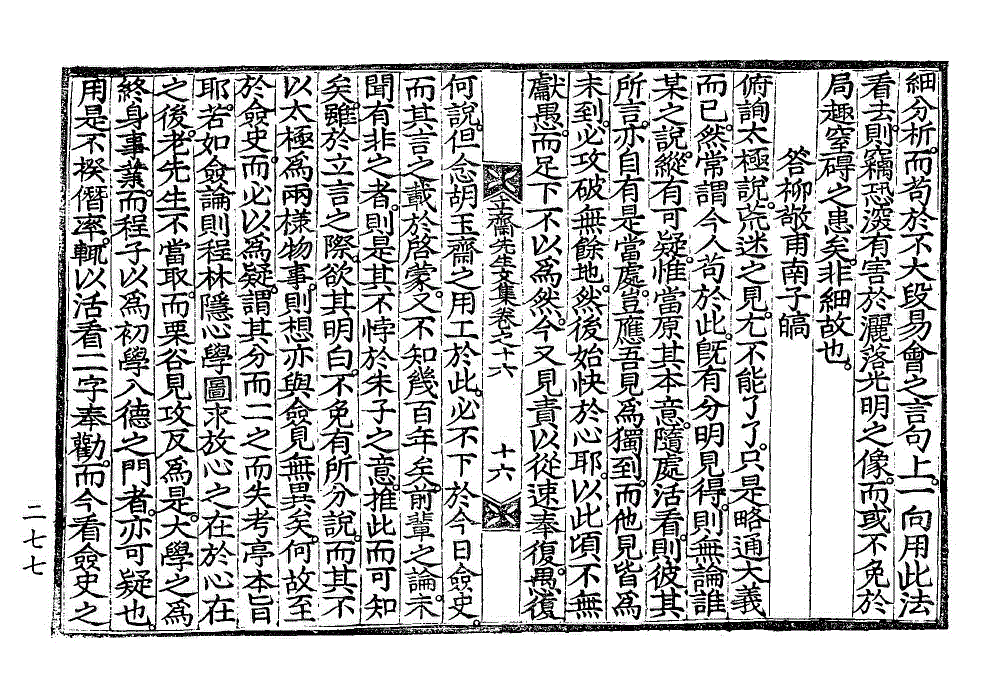 细分析。而苟于不大段易会之言句上。一向用此法看去。则窃恐深有害于洒落光明之像。而或不免于局趣窒碍之患矣。非细故也。
细分析。而苟于不大段易会之言句上。一向用此法看去。则窃恐深有害于洒落光明之像。而或不免于局趣窒碍之患矣。非细故也。答柳敬甫南子皓
俯询太极说。荒迷之见。尤不能了了。只是略通大义而已。然常谓今人苟于此。既有分明见得。则无论谁某之说。纵有可疑。惟当原其本意。随处活看。则彼其所言。亦自有是当处。岂应吾见为独到。而他见皆为未到。必攻破无馀地。然后始快于心耶。以此顷不无献愚。而足下不以为然。今又见责以从速奉复。愚复何说。但念胡玉斋之用工于此。必不下于今日佥史。而其言之载于启蒙。又不知几百年矣。前辈之论。未闻有非之者。则是其不悖于朱子之意。推此而可知矣。虽于立言之际。欲其明白。不免有所分说。而其不以太极为两样物事。则想亦与佥见无异矣。何故至于佥史。而必以为疑。谓其分而二之而失考亭本旨耶。若如佥论则程林隐心学图求放心之在于心在之后。老先生不当取。而栗谷见攻反为是。大学之为终身事业。而程子以为初学入德之门者。亦可疑也。用是不揆僭率。辄以活看二字奉劝。而今看佥史之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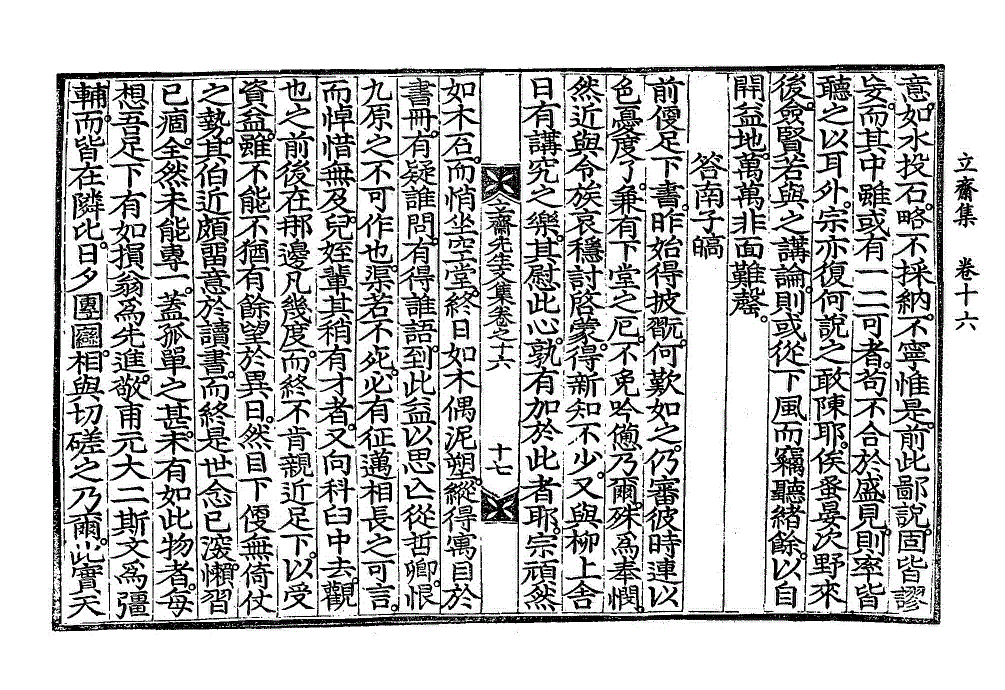 意。如水投石。略不采纳。不宁惟是。前此鄙说。固皆谬妄。而其中虽或有一二可者。苟不合于盛见。则率皆听之以耳外。宗亦复何说之敢陈耶。俟蚤晏次野来后。佥贤若与之讲论。则或从下风而窃听绪馀。以自开益地。万万非面难罄。
意。如水投石。略不采纳。不宁惟是。前此鄙说。固皆谬妄。而其中虽或有一二可者。苟不合于盛见。则率皆听之以耳外。宗亦复何说之敢陈耶。俟蚤晏次野来后。佥贤若与之讲论。则或从下风而窃听绪馀。以自开益地。万万非面难罄。答南子皓
前便足下书。昨始得披玩。何叹如之。仍审彼时连以色忧度了。兼有下堂之厄。不免吟惫乃尔。殊为奉悯。然近与令族哀稳讨启蒙。得新知不少。又与柳上舍日有讲究之乐。其慰此心。孰有加于此者耶。宗顽然如木石。而悄坐空堂。终日如木偶泥塑。纵得寓目于书册。有疑谁问。有得谁语。到此益以思亡从哲卿。恨九原之不可作也。渠若不死。必有征迈相长之可言。而悼惜无及。儿侄辈其稍有才者。又向科臼中去。观也之前后在那边凡几度。而终不肯亲近足下。以受资益。虽不能不犹有馀望于异日。然目下便无倚仗之势。其伯近颇留意于读书。而终是世念已深。懒习已痼。全然未能专一。盖孤单之甚。未有如此物者。每想吾足下有如损翁为先进。敬甫元大二斯文为彊辅。而皆在邻比。日夕团圞。相与切磋之乃尔。此实天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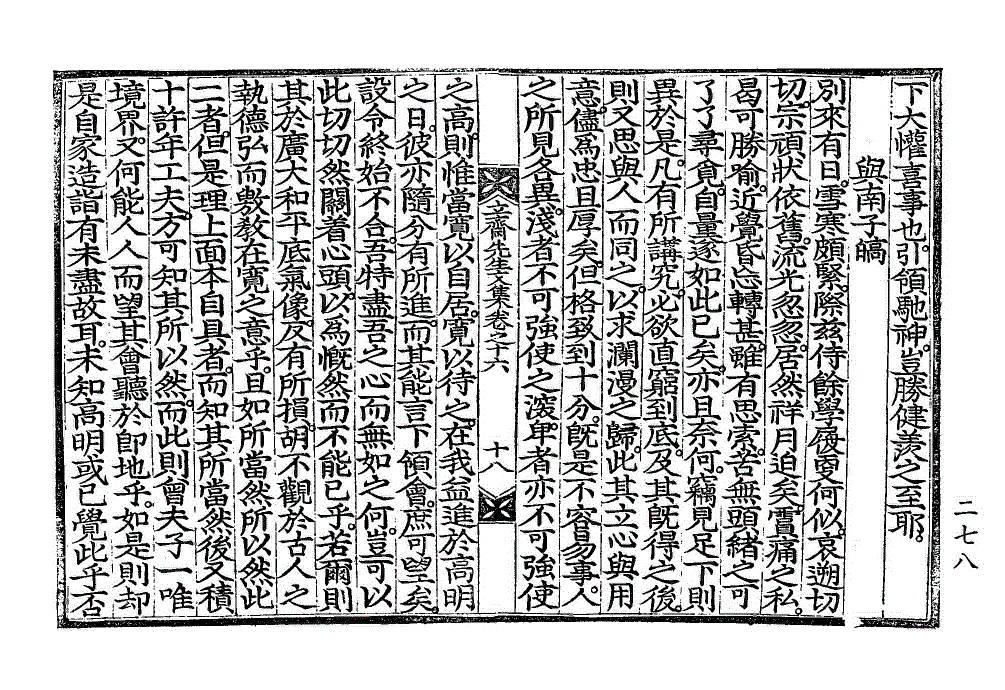 下大欢喜事也。引领驰神。岂胜健羡之至耶。
下大欢喜事也。引领驰神。岂胜健羡之至耶。与南子皓
别来有日。雪寒颇紧。际玆侍馀学履更何似。哀溯切切。宗顽状依旧。流光忽忽。居然祥月迫矣。霣痛之私。曷可胜喻。近觉昏忘转甚。虽有思索。苦无头绪之可了了寻觅。自量遂如此已矣。亦且奈何。窃见足下则异于是。凡有所讲究。必欲直穷到底。及其既得之后。则又思与人而同之。以求澜漫之归。此其立心与用意。尽为忠且厚矣。但格致到十分。既是不容易事。人之所见各异。浅者不可强使之深。卑者亦不可强使之高。则惟当宽以自居。宽以待之。在我益进于高明之日。彼亦随分有所进。而其能言下领会。庶可望矣。设令终始不合。吾特尽吾之心而无如之何。岂可以此切切然关着心头。以为慨然而不能已乎。若尔则其于广大和平底气像。反有所损。胡不观于古人之执德弘而敷教在宽之意乎。且如所当然所以然此二者。但是理上面本自具者。而知其所当然后又积十许年工夫。方可知其所以然。而此则曾夫子一唯境界。又何能人人而望其会听于即地乎。如是则却是自家造诣有未尽故耳。未知高明或已觉此乎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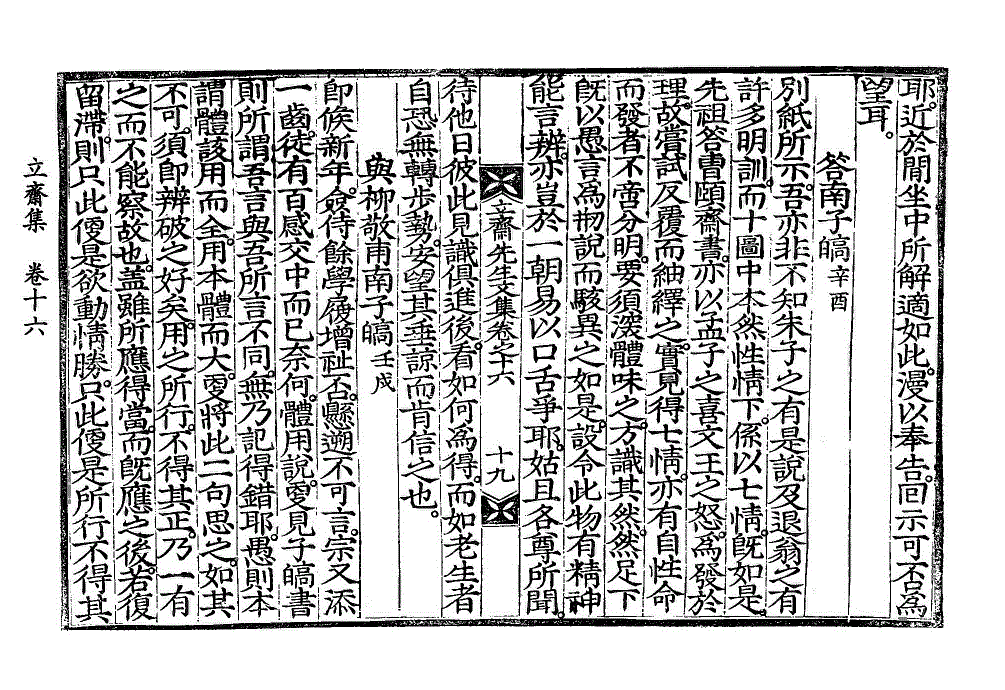 耶。近于閒坐中所解适如此。漫以奉告。回示可否为望耳。
耶。近于閒坐中所解适如此。漫以奉告。回示可否为望耳。答南子皓(辛酉)
别纸所示。吾亦非不知朱子之有是说及退翁之有许多明训。而十图中本然性情下。系以七情。既如是。先祖答曹颐斋书。亦以孟子之喜文王之怒。为发于理。故尝试反覆而䌷绎之。实见得七情。亦有自性命而发者不啻分明。要须深体味之。方识其然。然足下既以愚言为刱说而骇异之如是。设令此物有精神能言辨。亦岂于一朝易以口舌争耶。姑且各尊所闻。待他日彼此见识俱进后。看如何为得。而如老生者自恐无转步势。安望其垂谅而肯信之也。
与柳敬甫南子皓(壬戌)
即候新年。佥侍馀学履增祉否。悬溯不可言。宗又添一齿。徒有百感交中而已奈何。体用说。更见子皓书则所谓吾言与吾所言不同。无乃记得错耶。愚则本谓体该用而全。用本体而大。更将此二句思之。如其不可。须即辨破之好矣。用之所行。不得其正。乃一有之而不能察故也。盖虽所应得当。而既应之后。若复留滞。则只此便是欲动情胜。只此便是所行不得其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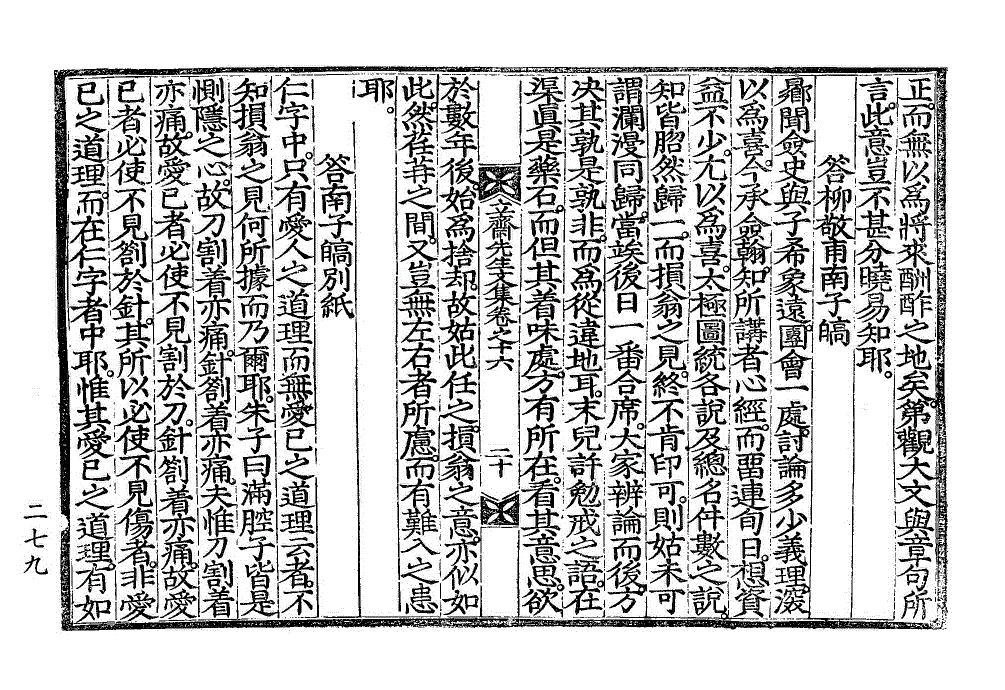 正。而无以为将来酬酢之地矣。第观大文与章句所言。此意岂不甚分晓易知耶。
正。而无以为将来酬酢之地矣。第观大文与章句所言。此意岂不甚分晓易知耶。答柳敬甫南子皓
向闻佥史与子希象远。团会一处。讨论多少义理。深以为喜。今承佥翰。知所讲者心经。而留连旬日。想资益不少。尤以为喜。太极图统各说及总名件数之说。知皆吻然归一。而损翁之见。终不肯印可。则姑未可谓澜漫同归。当俟后日一番合席。大家辨论而后。方决其孰是孰非。而为从违地耳。末儿许勉戒之语。在渠真是药石。而但其着味处。方有所在。看其意思。欲于数年后。始为舍却。故姑此任之。损翁之意。亦似如此。然荏苒之间。又岂无左右者所虑。而有难入之患耶。
答南子皓别纸
仁字中。只有爱人之道理而无爱己之道理云者。不知损翁之见何所据而乃尔耶。朱子曰满腔子皆是恻隐之心。故刀割着亦痛。针劄着亦痛。夫惟刀割着亦痛。故爱己者必使不见割于刀。针劄着亦痛。故爱己者必使不见劄于针。其所以必使不见伤者。非爱己之道理。而在仁字者中耶。惟其爱己之道理。有如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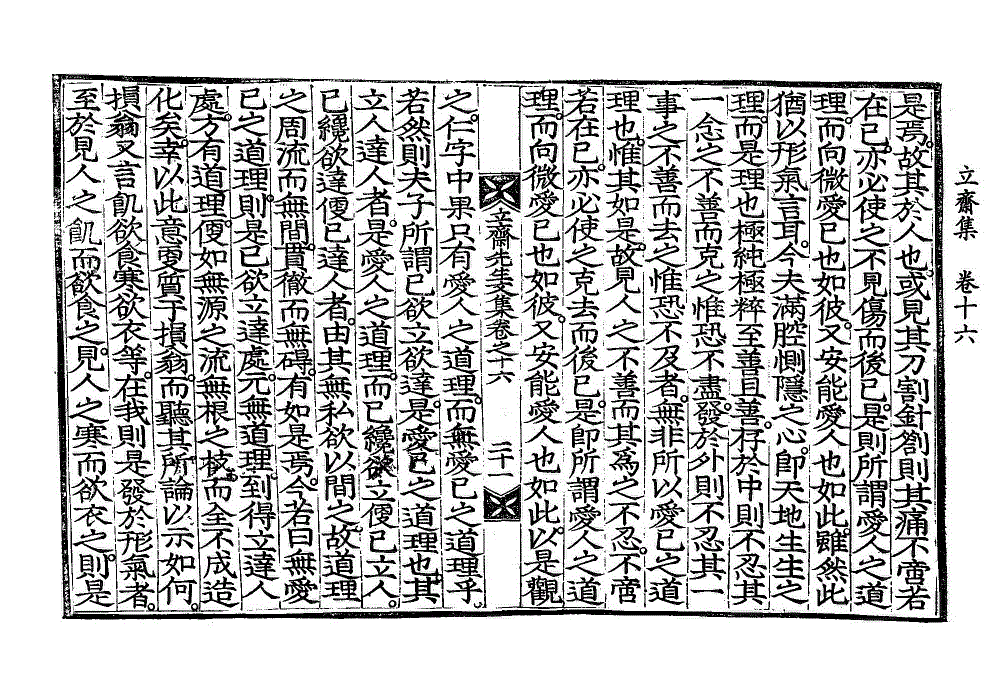 是焉。故其于人也。或见其刀割针劄则其痛不啻若在己。亦必使之不见伤而后已。是则所谓爱人之道理。而向微爱己也如彼。又安能爱人也如此。虽然此犹以形气言耳。今夫满腔恻隐之心。即天地生生之理。而是理也极纯极粹至善且善。存于中则不忍其一念之不善而克之惟恐不尽。发于外则不忍其一事之不善而去之惟恐不及者。无非所以爱己之道理也。惟其如是。故见人之不善而其为之不忍。不啻若在己。亦必使之克去而后已。是即所谓爱人之道理。而向微爱己也如彼。又安能爱人也如此。以是观之。仁字中果只有爱人之道理。而无爱己之道理乎。若然则夫子所谓己欲立欲达。是爱己之道理也。其立人达人者。是爱人之道理。而己才欲立便已立人。己才欲达便已达人者。由其无私欲以间之。故道理之周流而无间。贯彻而无碍。有如是焉。今若曰无爱己之道理。则是己欲立达处。元无道理。到得立达人处。方有道理。便如无源之流无根之枝。而全不成造化矣。幸以此意更质于损翁。而听其所论以示如何。损翁又言饥欲食寒欲衣等。在我则是发于形气者。至于见人之饥而欲食之。见人之寒而欲衣之。则是
是焉。故其于人也。或见其刀割针劄则其痛不啻若在己。亦必使之不见伤而后已。是则所谓爱人之道理。而向微爱己也如彼。又安能爱人也如此。虽然此犹以形气言耳。今夫满腔恻隐之心。即天地生生之理。而是理也极纯极粹至善且善。存于中则不忍其一念之不善而克之惟恐不尽。发于外则不忍其一事之不善而去之惟恐不及者。无非所以爱己之道理也。惟其如是。故见人之不善而其为之不忍。不啻若在己。亦必使之克去而后已。是即所谓爱人之道理。而向微爱己也如彼。又安能爱人也如此。以是观之。仁字中果只有爱人之道理。而无爱己之道理乎。若然则夫子所谓己欲立欲达。是爱己之道理也。其立人达人者。是爱人之道理。而己才欲立便已立人。己才欲达便已达人者。由其无私欲以间之。故道理之周流而无间。贯彻而无碍。有如是焉。今若曰无爱己之道理。则是己欲立达处。元无道理。到得立达人处。方有道理。便如无源之流无根之枝。而全不成造化矣。幸以此意更质于损翁。而听其所论以示如何。损翁又言饥欲食寒欲衣等。在我则是发于形气者。至于见人之饥而欲食之。见人之寒而欲衣之。则是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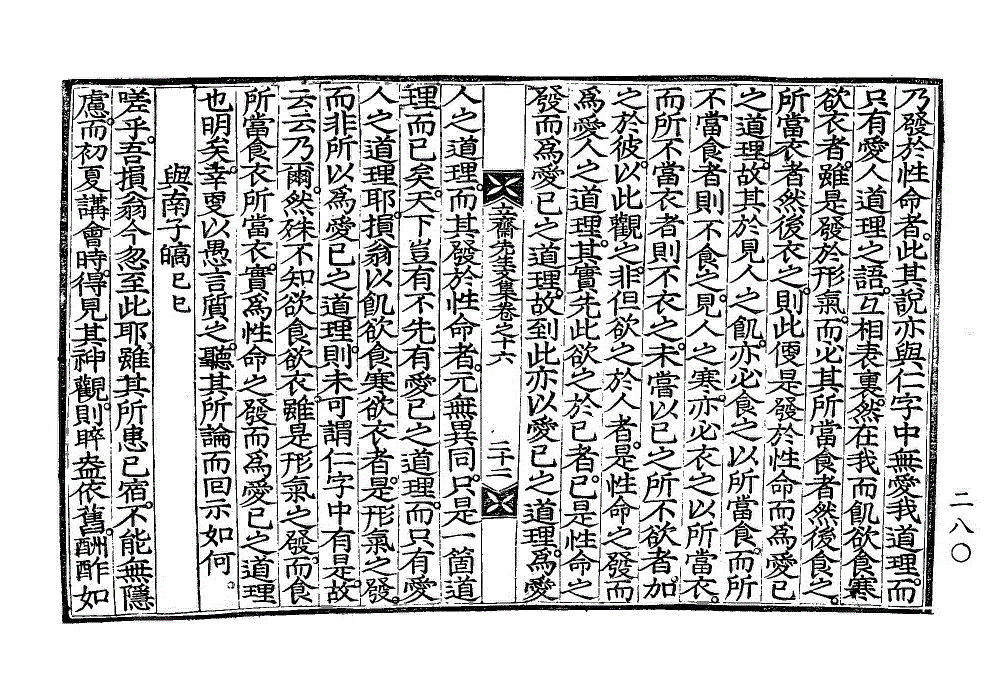 乃发于性命者。此其说亦与仁字中无爱我道理。而只有爱人道理之语。互相表里。然在我而饥欲食寒欲衣者。虽是发于形气。而必其所当食者然后食之。所当衣者然后衣之。则此便是发于性命而为爱己之道理。故其于见人之饥。亦必食之以所当食。而所不当食者则不食之。见人之寒。亦必衣之以所当衣。而所不当衣者则不衣之。未尝以己之所不欲者。加之于彼。以此观之。非但欲之于人者。是性命之发而为爱人之道理。其实先此欲之于己者。已是性命之发而为爱己之道理。故到此亦以爱己之道理。为爱人之道理。而其发于性命者。元无异同。只是一个道理而已矣。天下岂有不先有爱己之道理。而只有爱人之道理耶。损翁以饥欲食寒欲衣者。是形气之发。而非所以为爱己之道理。则未可谓仁字中有是。故云云乃尔。然殊不知欲食欲衣。虽是形气之发。而食所当食衣所当衣。实为性命之发而为爱己之道理也明矣。幸更以愚言质之。听其所论而回示如何。
乃发于性命者。此其说亦与仁字中无爱我道理。而只有爱人道理之语。互相表里。然在我而饥欲食寒欲衣者。虽是发于形气。而必其所当食者然后食之。所当衣者然后衣之。则此便是发于性命而为爱己之道理。故其于见人之饥。亦必食之以所当食。而所不当食者则不食之。见人之寒。亦必衣之以所当衣。而所不当衣者则不衣之。未尝以己之所不欲者。加之于彼。以此观之。非但欲之于人者。是性命之发而为爱人之道理。其实先此欲之于己者。已是性命之发而为爱己之道理。故到此亦以爱己之道理。为爱人之道理。而其发于性命者。元无异同。只是一个道理而已矣。天下岂有不先有爱己之道理。而只有爱人之道理耶。损翁以饥欲食寒欲衣者。是形气之发。而非所以为爱己之道理。则未可谓仁字中有是。故云云乃尔。然殊不知欲食欲衣。虽是形气之发。而食所当食衣所当衣。实为性命之发而为爱己之道理也明矣。幸更以愚言质之。听其所论而回示如何。与南子皓(己巳)
嗟乎。吾损翁今忽至此耶。虽其所患已宿。不能无隐虑。而初夏讲会时。得见其神观。则睟盎依旧。酬酢如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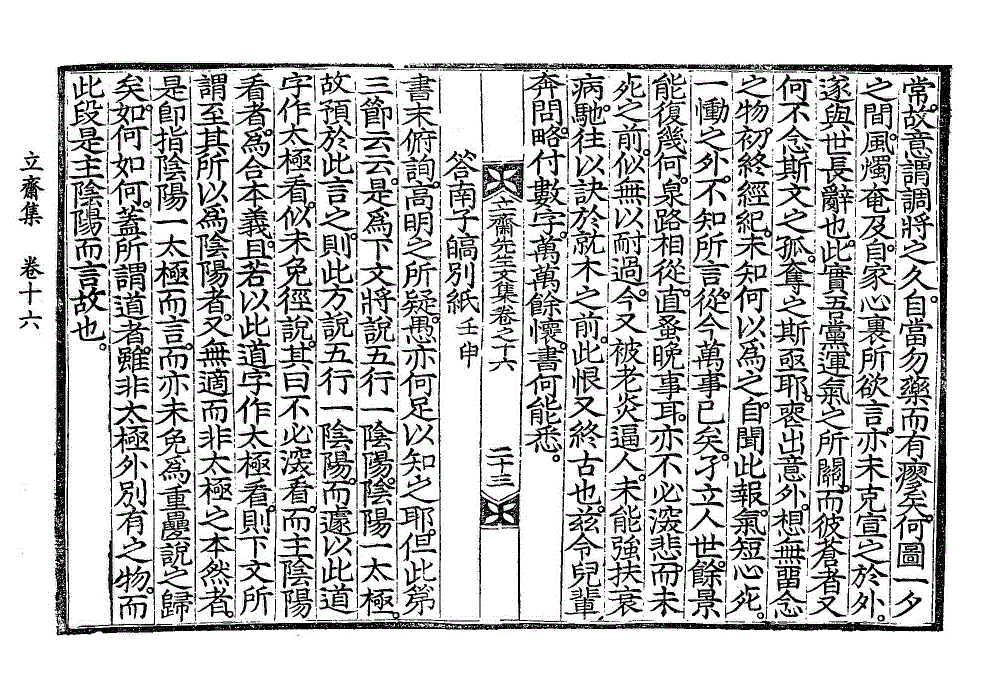 常。故意谓调将之久。自当勿药而有瘳矣。何图一夕之间。风烛奄及。自家心里所欲言。亦未克宣之于外。遂与世长辞也。此实吾党运气之所关。而彼苍者又何不念斯文之孤。夺之斯亟耶。丧出意外。想无留念之物。初终经纪。未知何以为之。自闻此报。气短心死。一恸之外。不知所言。从今万事已矣。孑立人世。馀景能复几何。泉路相从。直蚤晚事耳。亦不必深悲。而未死之前。似无以耐过。今又被老炎逼人。未能强扶衰病。驰往以诀于就木之前。此恨又终古也。玆令儿辈奔问。略付数字。万万馀怀。书何能悉。
常。故意谓调将之久。自当勿药而有瘳矣。何图一夕之间。风烛奄及。自家心里所欲言。亦未克宣之于外。遂与世长辞也。此实吾党运气之所关。而彼苍者又何不念斯文之孤。夺之斯亟耶。丧出意外。想无留念之物。初终经纪。未知何以为之。自闻此报。气短心死。一恸之外。不知所言。从今万事已矣。孑立人世。馀景能复几何。泉路相从。直蚤晚事耳。亦不必深悲。而未死之前。似无以耐过。今又被老炎逼人。未能强扶衰病。驰往以诀于就木之前。此恨又终古也。玆令儿辈奔问。略付数字。万万馀怀。书何能悉。答南子皓别纸(壬申)
书末俯询。高明之所疑。愚亦何足以知之耶。但此第三节云云。是为下文将说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故预于此言之。则此方说五行一阴阳。而遽以此道字作太极看。似未免径说。其曰不必深看。而主阴阳看者。为合本义。且若以此道字作太极看。则下文所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者。是即指阴阳一太极而言。而亦未免为重叠说之归矣。如何如何。盖所谓道者。虽非太极外别有之物。而此段是主阴阳而言故也。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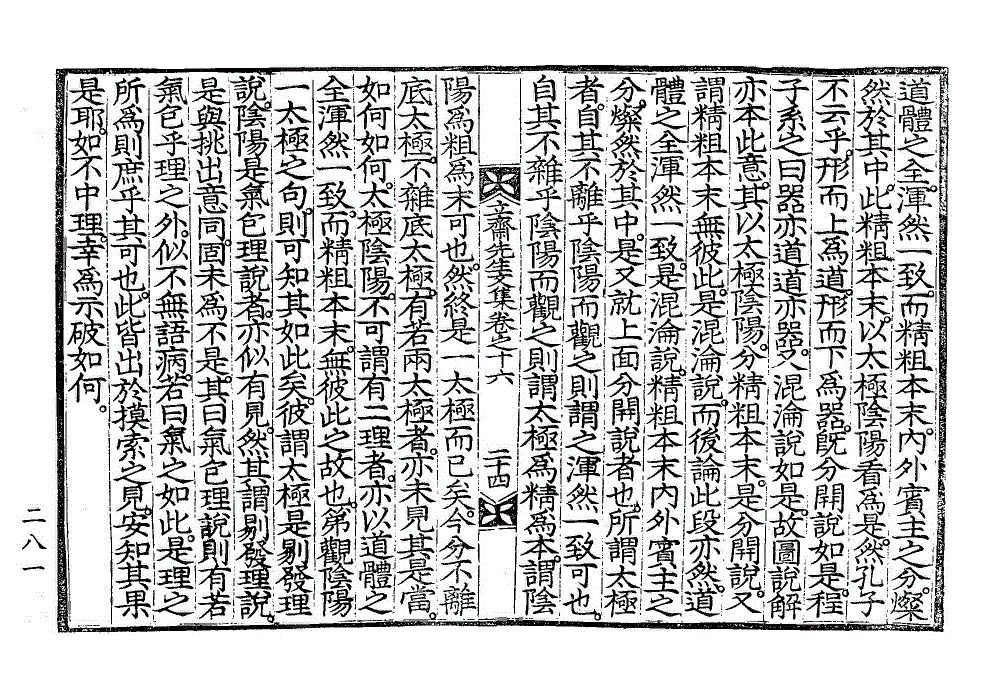 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灿然于其中。此精粗本末。以太极阴阳看为是。然孔子不云乎。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既分开说如是。程子系之曰器亦道道亦器。又混沦说如是。故图说解亦本此意。其以太极阴阳。分精粗本末。是分开说。又谓精粗本末无彼此。是混沦说。而后论此段亦然。道体之全浑然一致。是混沦说。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灿然于其中。是又就上面分开说者也。所谓太极者。自其不离乎阴阳而观之则谓之浑然一致可也。自其不杂乎阴阳而观之则谓太极为精为本。谓阴阳为粗为末可也。然终是一太极而已矣。今分不离底太极。不杂底太极。有若两太极者。亦未见其是当。如何如何。太极阴阳。不可谓有二理者。亦以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无彼此之故也。第观阴阳一太极之句。则可知其如此矣。彼谓太极是剔发理说。阴阳是气包理说者。亦似有见。然其谓剔发理说。是与挑出意同。固未为不是。其曰气包理说则有若气包乎理之外。似不无语病。若曰气之如此。是理之所为则庶乎其可也。此皆出于摸索之见。安知其果是耶。如不中理。幸为示破如何。
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灿然于其中。此精粗本末。以太极阴阳看为是。然孔子不云乎。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既分开说如是。程子系之曰器亦道道亦器。又混沦说如是。故图说解亦本此意。其以太极阴阳。分精粗本末。是分开说。又谓精粗本末无彼此。是混沦说。而后论此段亦然。道体之全浑然一致。是混沦说。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灿然于其中。是又就上面分开说者也。所谓太极者。自其不离乎阴阳而观之则谓之浑然一致可也。自其不杂乎阴阳而观之则谓太极为精为本。谓阴阳为粗为末可也。然终是一太极而已矣。今分不离底太极。不杂底太极。有若两太极者。亦未见其是当。如何如何。太极阴阳。不可谓有二理者。亦以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无彼此之故也。第观阴阳一太极之句。则可知其如此矣。彼谓太极是剔发理说。阴阳是气包理说者。亦似有见。然其谓剔发理说。是与挑出意同。固未为不是。其曰气包理说则有若气包乎理之外。似不无语病。若曰气之如此。是理之所为则庶乎其可也。此皆出于摸索之见。安知其果是耶。如不中理。幸为示破如何。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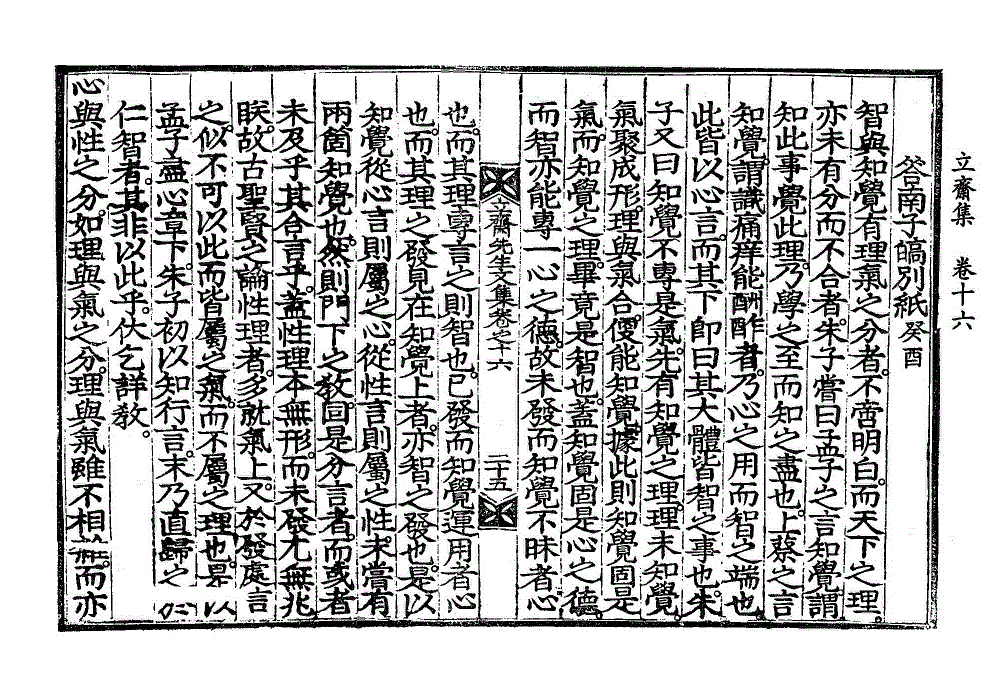 答南子皓别纸(癸酉)
答南子皓别纸(癸酉)智与知觉有理气之分者。不啻明白。而天下之理。亦未有分而不合者。朱子尝曰孟子之言知觉。谓知此事觉此理。乃学之至而知之尽也。上蔡之言知觉。谓识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此皆以心言。而其下即曰其大体皆智之事也。朱子又曰知觉不专是气。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据此则知觉固是气。而知觉之理。毕竟是智也。盖知觉固是心之德。而智亦能专一心之德。故未发而知觉不昧者心也。而其理专言之则智也。已发而知觉运用者心也。而其理之发见在知觉上者。亦智之发也。是以知觉从心言则属之心。从性言则属之性。未尝有两个知觉也。然则门下之教。固是分言者。而或者未及乎其合言乎。盖性理本无形。而未发尤无兆眹。故古圣贤之论性理者。多就气上。又于发处言之。似不可以此而皆属之气。而不属之理也。是以孟子尽心章下。朱子初以知行言。末乃直归之于仁智者。其非以此乎。伏乞详教。
心与性之分。如理与气之分。理与气虽不相杂。而亦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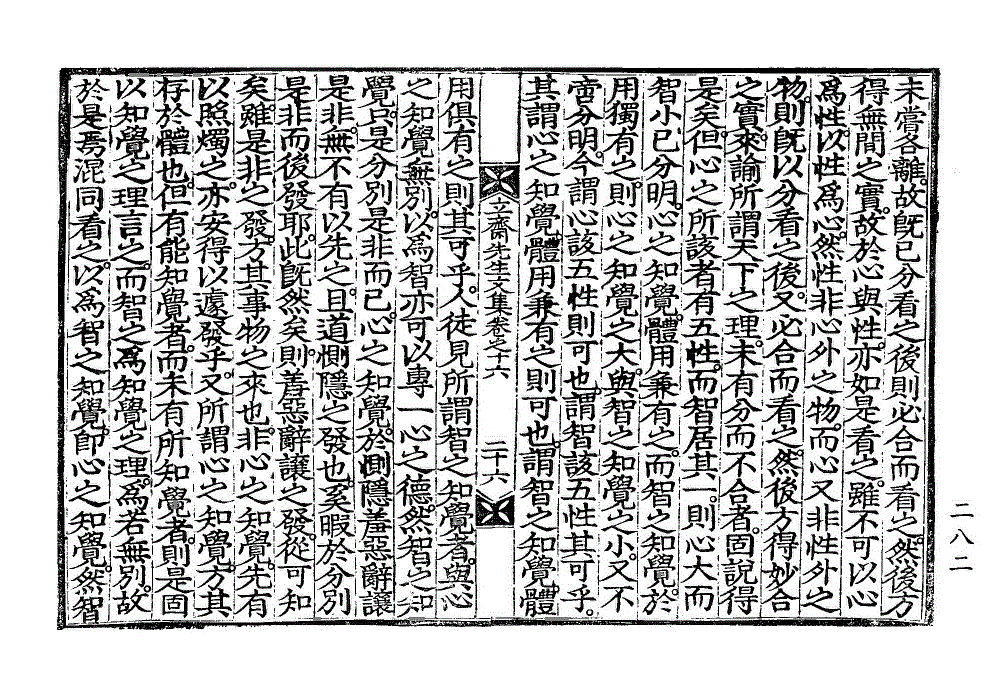 未尝各离。故既已分看之后则必合而看之。然后方得无间之实。故于心与性。亦如是看之。虽不可以心为性。以性为心。然性非心外之物。而心又非性外之物。则既以分看之后。又必合而看之。然后方得妙合之实。来谕所谓天下之理。未有分而不合者。固说得是矣。但心之所该者有五性。而智居其一。则心大而智小已分明。心之知觉。体用兼有之。而智之知觉。于用独有之。则心之知觉之大。与智之知觉之小。又不啻分明。今谓心该五性则可也。谓智该五性其可乎。其谓心之知觉。体用兼有之则可也。谓智之知觉。体用俱有之则其可乎。人徒见所谓智之知觉者。与心之知觉无别。以为智亦可以专一心之德。然智之知觉。只是分别是非而已。心之知觉。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不有以先之。且道恻隐之发也。奚暇于分别是非而后发耶。此既然矣。则羞恶辞让之发。从可知矣。虽是非之发。方其事物之来也。非心之知觉。先有以照烛之。亦安得以遽发乎。又所谓心之知觉。方其存于体也。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者。则是固以知觉之理言之。而智之为知觉之理。为若无别。故于是焉混同看之。以为智之知觉。即心之知觉。然智
未尝各离。故既已分看之后则必合而看之。然后方得无间之实。故于心与性。亦如是看之。虽不可以心为性。以性为心。然性非心外之物。而心又非性外之物。则既以分看之后。又必合而看之。然后方得妙合之实。来谕所谓天下之理。未有分而不合者。固说得是矣。但心之所该者有五性。而智居其一。则心大而智小已分明。心之知觉。体用兼有之。而智之知觉。于用独有之。则心之知觉之大。与智之知觉之小。又不啻分明。今谓心该五性则可也。谓智该五性其可乎。其谓心之知觉。体用兼有之则可也。谓智之知觉。体用俱有之则其可乎。人徒见所谓智之知觉者。与心之知觉无别。以为智亦可以专一心之德。然智之知觉。只是分别是非而已。心之知觉。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不有以先之。且道恻隐之发也。奚暇于分别是非而后发耶。此既然矣。则羞恶辞让之发。从可知矣。虽是非之发。方其事物之来也。非心之知觉。先有以照烛之。亦安得以遽发乎。又所谓心之知觉。方其存于体也。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者。则是固以知觉之理言之。而智之为知觉之理。为若无别。故于是焉混同看之。以为智之知觉。即心之知觉。然智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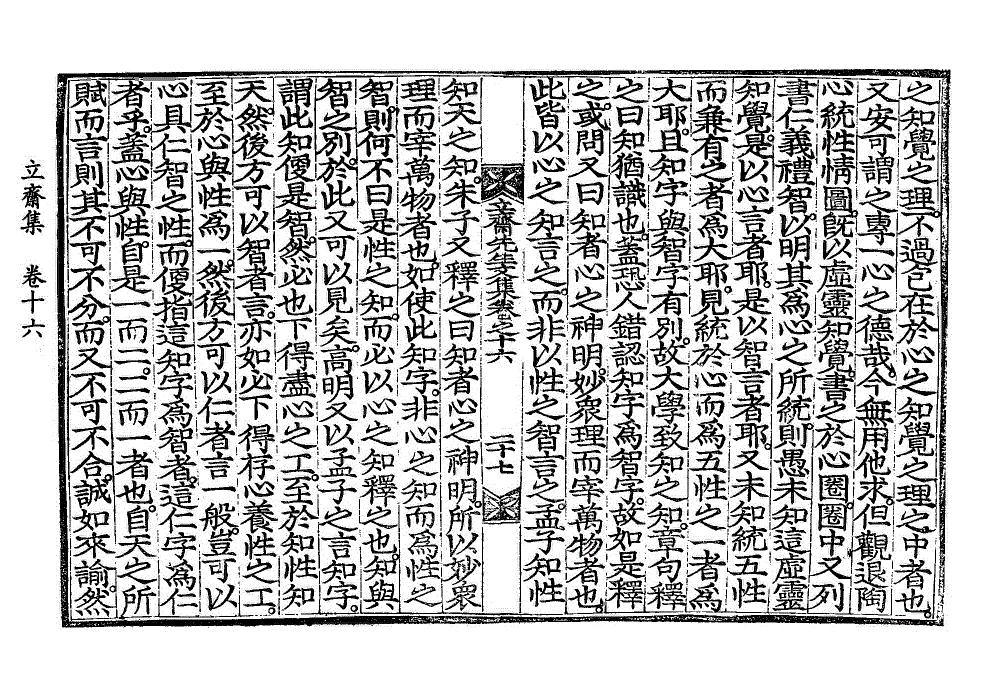 之知觉之理。不过包在于心之知觉之理之中者也。又安可谓之专一心之德哉。今无用他求。但观退陶心统性情图。既以虚灵知觉。书之于心圈。圈中又列书仁义礼智。以明其为心之所统。则愚未知这虚灵知觉。是以心言者耶。是以智言者耶。又未知统五性而兼有之者为大耶。见统于心而为五性之一者为大耶。且知字与智字有别。故大学致知之知。章句释之曰知犹识也。盖恐人错认知字为智字。故如是释之。或问又曰知者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此皆以心之知言之。而非以性之智言之。孟子知性知天之知。朱子又释之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如使此知字。非心之知而为性之智。则何不曰是性之知。而必以心之知释之也。知与智之别。于此又可以见矣。高明又以孟子之言知字。谓此知便是智。然必也下得尽心之工。至于知性知天。然后方可以智者言。亦如必下得存心养性之工。至于心与性为一。然后方可以仁者言一般。岂可以心具仁智之性。而便指这知字为智者。这仁字为仁者乎。盖心与性。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天之所赋而言则其不可不分。而又不可不合。诚如来谕。然
之知觉之理。不过包在于心之知觉之理之中者也。又安可谓之专一心之德哉。今无用他求。但观退陶心统性情图。既以虚灵知觉。书之于心圈。圈中又列书仁义礼智。以明其为心之所统。则愚未知这虚灵知觉。是以心言者耶。是以智言者耶。又未知统五性而兼有之者为大耶。见统于心而为五性之一者为大耶。且知字与智字有别。故大学致知之知。章句释之曰知犹识也。盖恐人错认知字为智字。故如是释之。或问又曰知者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此皆以心之知言之。而非以性之智言之。孟子知性知天之知。朱子又释之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如使此知字。非心之知而为性之智。则何不曰是性之知。而必以心之知释之也。知与智之别。于此又可以见矣。高明又以孟子之言知字。谓此知便是智。然必也下得尽心之工。至于知性知天。然后方可以智者言。亦如必下得存心养性之工。至于心与性为一。然后方可以仁者言一般。岂可以心具仁智之性。而便指这知字为智者。这仁字为仁者乎。盖心与性。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天之所赋而言则其不可不分。而又不可不合。诚如来谕。然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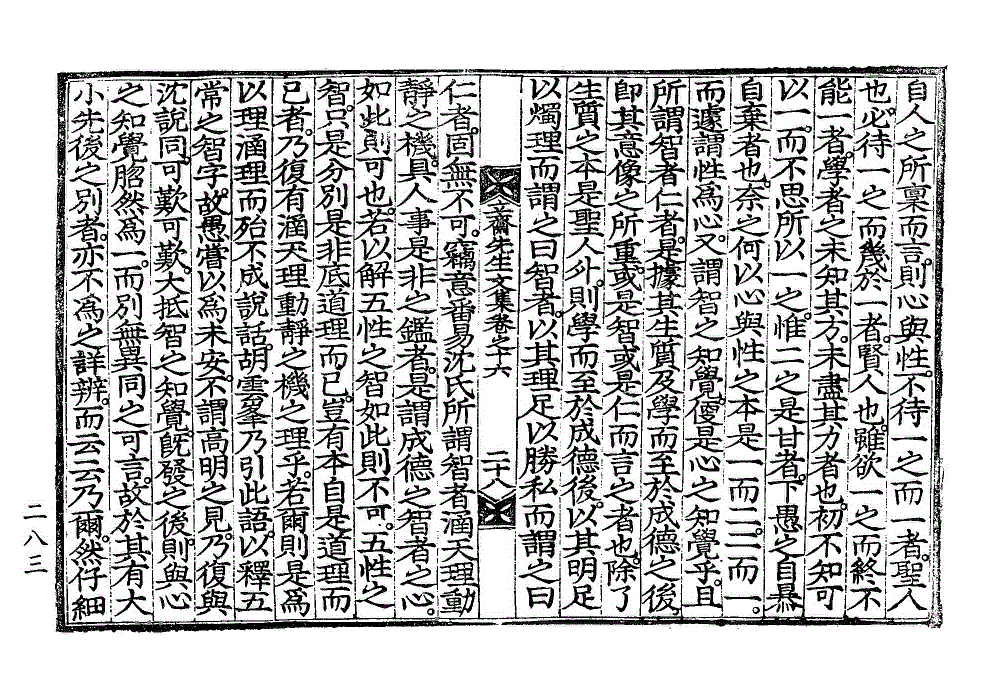 自人之所禀而言。则心与性。不待一之而一者。圣人也。必待一之而几于一者。贤人也。虽欲一之而终不能一者。学者之未知其方。未尽其力者也。初不知可以一。而不思所以一之。惟二之是甘者。下愚之自暴自弃者也。奈之何以心与性之本是一而二。二而一。而遽谓性为心。又谓智之知觉。便是心之知觉乎。且所谓智者仁者。是据其生质及学而至于成德之后。即其意像之所重。或是智或是仁而言之者也。除了生质之本是圣人外。则学而至于成德后。以其明足以烛理而谓之曰智者。以其理足以胜私而谓之曰仁者。固无不可。窃意番易沈氏所谓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者。是谓成德之智者之心。如此则可也。若以解五性之智如此则不可。五性之智。只是分别是非底道理而已。岂有本自是道理而已者。乃复有涵天理动静之机之理乎。若尔则是为以理涵理而殆不成说话。胡云峰乃引此语。以释五常之智字。故愚尝以为未安。不谓高明之见。乃复与沈说同。可叹可叹。大抵智之知觉。既发之后。则与心之知觉吻然为一。而别无异同之可言。故于其有大小先后之别者。亦不为之详辨。而云云乃尔。然仔细
自人之所禀而言。则心与性。不待一之而一者。圣人也。必待一之而几于一者。贤人也。虽欲一之而终不能一者。学者之未知其方。未尽其力者也。初不知可以一。而不思所以一之。惟二之是甘者。下愚之自暴自弃者也。奈之何以心与性之本是一而二。二而一。而遽谓性为心。又谓智之知觉。便是心之知觉乎。且所谓智者仁者。是据其生质及学而至于成德之后。即其意像之所重。或是智或是仁而言之者也。除了生质之本是圣人外。则学而至于成德后。以其明足以烛理而谓之曰智者。以其理足以胜私而谓之曰仁者。固无不可。窃意番易沈氏所谓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者。是谓成德之智者之心。如此则可也。若以解五性之智如此则不可。五性之智。只是分别是非底道理而已。岂有本自是道理而已者。乃复有涵天理动静之机之理乎。若尔则是为以理涵理而殆不成说话。胡云峰乃引此语。以释五常之智字。故愚尝以为未安。不谓高明之见。乃复与沈说同。可叹可叹。大抵智之知觉。既发之后。则与心之知觉吻然为一。而别无异同之可言。故于其有大小先后之别者。亦不为之详辨。而云云乃尔。然仔细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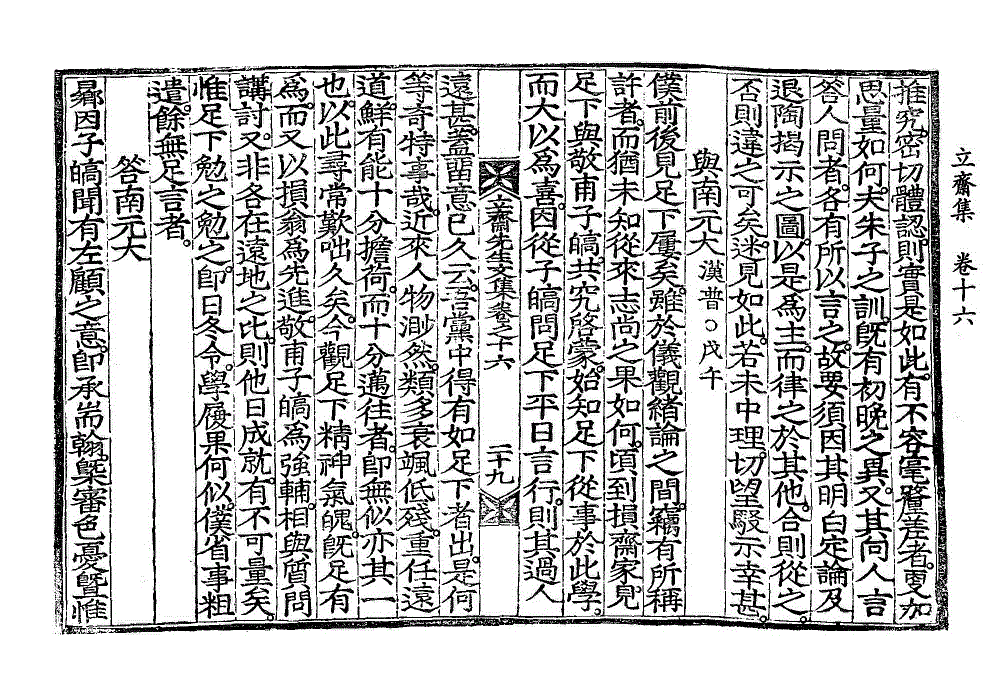 推究。密切体认。则实是如此。有不容毫釐差者。更加思量如何。夫朱子之训。既有初晚之异。又其向人言答人问者。各有所以言之。故要须因其明白定论及退陶揭示之图。以是为主。而律之于其他。合则从之。否则违之可矣。迷见如此。若未中理。切望驳示幸甚。
推究。密切体认。则实是如此。有不容毫釐差者。更加思量如何。夫朱子之训。既有初晚之异。又其向人言答人问者。各有所以言之。故要须因其明白定论及退陶揭示之图。以是为主。而律之于其他。合则从之。否则违之可矣。迷见如此。若未中理。切望驳示幸甚。与南元大(汉普○戊午)
仆前后见足下屡矣。虽于仪观绪论之间。窃有所称许者。而犹未知从来志尚之果如何。顷到损斋家。见足下与敬甫子皓。共究启蒙。始知足下从事于此学。而大以为喜。因从子皓问足下平日言行。则其过人远甚。盖留意已久云。吾党中得有如足下者出。是何等奇特事哉。近来人物渺然。类多衰飒低残。重任远道。鲜有能十分担荷。而十分迈往者。即无似亦其一也。以此寻常叹咄久矣。今观足下精神气魄。既足有为。而又以损翁为先进。敬甫子皓为强辅。相与质问讲讨。又非各在远地之比。则他日成就。有不可量矣。惟足下勉之勉之。即日冬令。学履果何似。仆省事粗遣。馀无足言者。
答南元大
向因子皓闻有左顾之意。即承耑翰。槩审色忧暨惟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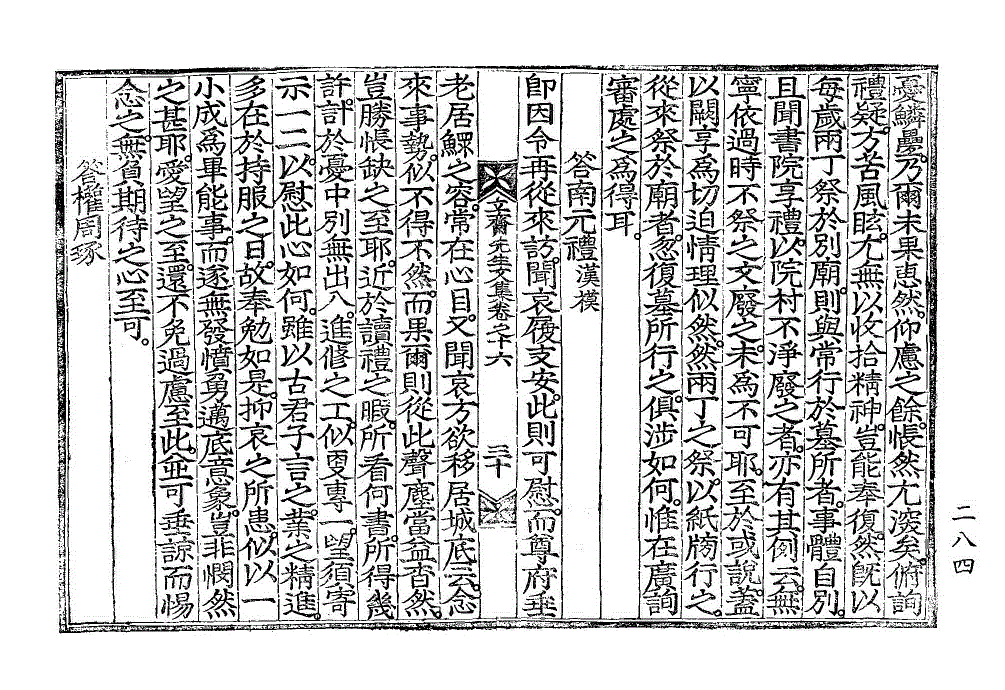 忧鳞叠。乃尔未果惠然。仰虑之馀。怅然尤深矣。俯询礼疑。方苦风眩。尤无以收拾精神。岂能奉复。然既以每岁两丁祭于别庙。则与常行于墓所者。事体自别。且闻书院享礼。以院村不净废之者。亦有其例云。无宁依过时不祭之文废之。未为不可耶。至于或说。盖以阙享为切迫情理似然。然两丁之祭。以纸榜行之。从来祭于庙者。忽复墓所行之。俱涉如何。惟在广询审处之为得耳。
忧鳞叠。乃尔未果惠然。仰虑之馀。怅然尤深矣。俯询礼疑。方苦风眩。尤无以收拾精神。岂能奉复。然既以每岁两丁祭于别庙。则与常行于墓所者。事体自别。且闻书院享礼。以院村不净废之者。亦有其例云。无宁依过时不祭之文废之。未为不可耶。至于或说。盖以阙享为切迫情理似然。然两丁之祭。以纸榜行之。从来祭于庙者。忽复墓所行之。俱涉如何。惟在广询审处之为得耳。答南元礼(汉模)
即因令再从来访。闻哀履支安。此则可慰。而尊府垂老居鳏之容。常在心目。又闻哀方欲移居城底云。念来事势。似不得不然。而果尔则从此声尘当益杳然。岂胜怅缺之至耶。近于读礼之暇。所看何书。所得几许。计于忧中别无出入。进修之工。似更专一。望须寄示一二。以慰此心如何。虽以古君子言之。业之精进。多在于持服之日。故奉勉如是。抑哀之所患。似以一小成为毕能事。而遂无发愤勇迈底意象。岂非悯然之甚耶。爱望之至。还不免过虑至此。并可垂谅而惕念之。无负期待之心至可。
答权周琢
立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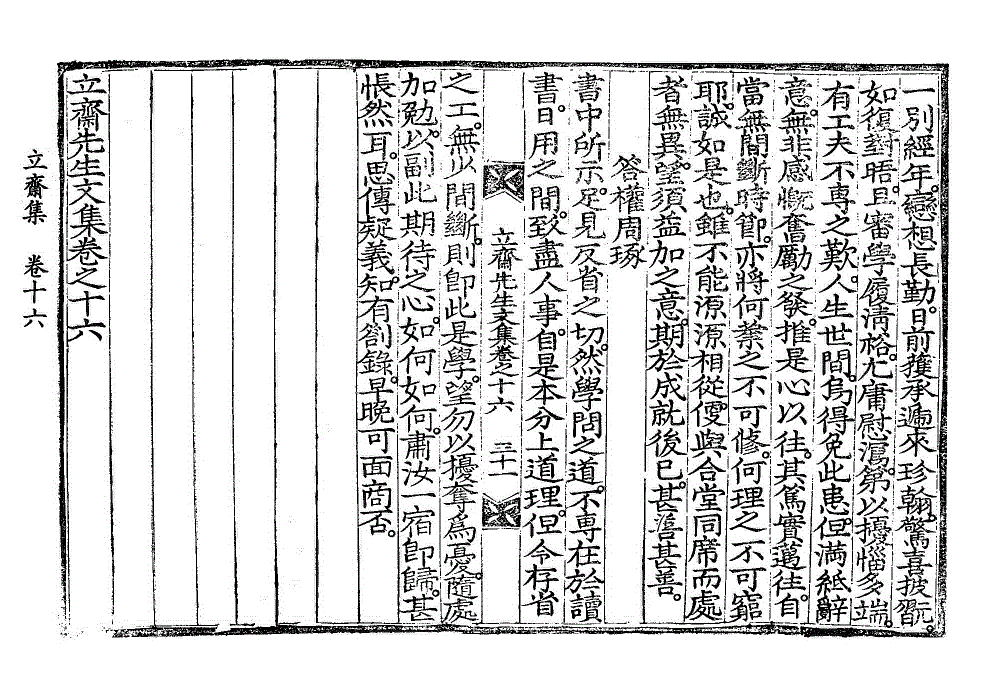 一别经年。恋想长勤。日前获承递来珍翰。惊喜披玩。如复对晤。且审学履清裕。尤庸慰泻。第以扰恼多端。有工夫不专之叹。人生世间。乌得免此患。但满纸辞意。无非感慨奋励之发。推是心以往。其笃实迈往。自当无间断时节。亦将何业之不可修。何理之不可穷耶。诚如是也。虽不能源源相从。便与合堂同席而处者无异。望须益加之意。期于成就后已。甚善甚善。
一别经年。恋想长勤。日前获承递来珍翰。惊喜披玩。如复对晤。且审学履清裕。尤庸慰泻。第以扰恼多端。有工夫不专之叹。人生世间。乌得免此患。但满纸辞意。无非感慨奋励之发。推是心以往。其笃实迈往。自当无间断时节。亦将何业之不可修。何理之不可穷耶。诚如是也。虽不能源源相从。便与合堂同席而处者无异。望须益加之意。期于成就后已。甚善甚善。答权周琢
书中所示。足见反省之切。然学问之道。不专在于读书。日用之间。致尽人事。自是本分上道理。但令存省之工。无少间断。则即此是学。望勿以扰夺为忧。随处加勉。以副此期待之心。如何如何。肃汝一宿即归。甚怅然耳。思传疑义。知有劄录。早晚可面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