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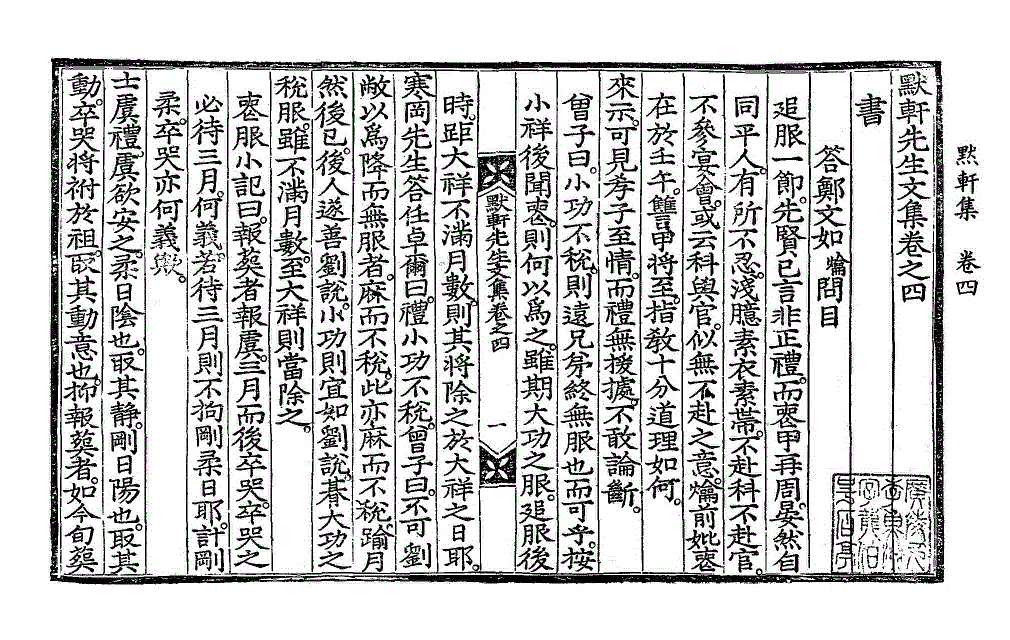 答郑文如(爚)问目
答郑文如(爚)问目追服一节。先贤已言非正礼。而丧甲再周。晏然自同平人。有所不忍。浅臆素衣素带。不赴科不赴官。不参宴会。或云科与官。似无不赴之意。爚前妣丧在于壬午。雠甲将至。指教十分道理如何。
来示。可见孝子至情。而礼无援据。不敢论断。
曾子曰。小功不税。则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按小祥后闻丧。则何以为之。虽期大功之服。追服后时。距大祥不满月数。则其将除之于大祥之日耶。
寒冈先生答任卓尔曰。礼小功不税。曾子曰。不可刘敝以为降而无服者。麻而不税。此亦麻而不税。踰月然后已。后人遂善刘说。小功则宜如刘说。期大功之税服。虽不满月数。至大祥则当除之。
丧服小记曰。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卒哭之必待三月。何义。若待三月则不拘刚柔日耶。计刚柔。卒哭亦何义欤。
士虞礼。虞欲安之。柔日阴也。取其静。刚日阳也。取其动。卒哭将祔于祖。取其动意也。抑报葬者。如今旬葬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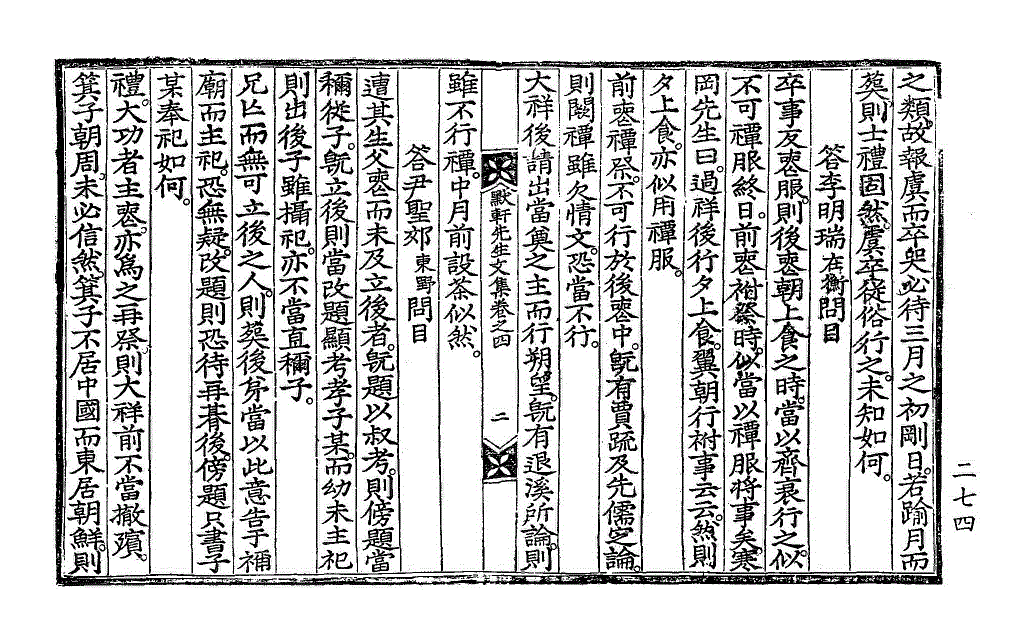 之类。故报虞而卒哭必待三月之初刚日。若踰月而葬。则士礼固然。虞卒从俗行之。未知如何。
之类。故报虞而卒哭必待三月之初刚日。若踰月而葬。则士礼固然。虞卒从俗行之。未知如何。答李明瑞(在衡)问目
卒事反丧服。则后丧朝上食之时。当以齐衰行之。似不可禫服终日。前丧祔祭时。似当以禫服将事矣。寒冈先生曰。过祥后行夕上食。翼朝行祔事云云。然则夕上食。亦似用禫服。
前丧禫祭。不可行于后丧中。既有贾疏及先儒定论。则阙禫虽欠情文。恐当不行。
大祥后请出当奠之主而行朔望。既有退溪所论。则虽不行禫。中月前设茶似然。
答尹圣郊(东野)问目
遭其生父丧而未及立后者。既题以叔考。则傍题当称从子。既立后则当改题显考孝子某。而幼未主祀则出后子虽摄祀。亦不当直称子。
兄亡而无可立后之人。则葬后弟当以此意告于祢庙而主祀。恐无疑。改题则恐待再期后。傍题只书子某奉祀如何。
礼。大功者主丧。亦为之再祭。则大祥前不当撤殡。
箕子朝周。未必信然。箕子不居中国而东居朝鲜。则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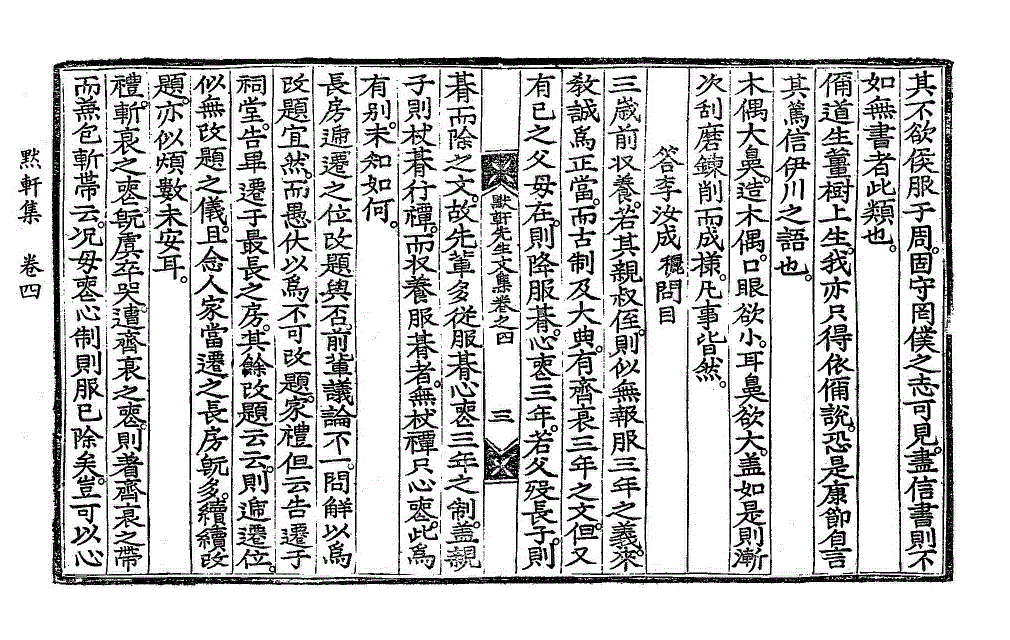 其不欲侯服于周。固守罔仆之志可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者此类也。
其不欲侯服于周。固守罔仆之志可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者此类也。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恐是康节自言其笃信伊川之语也。
木偶大鼻。造木偶。口眼欲小。耳鼻欲大。盖如是则渐次刮磨鍊削而成㨾。凡事皆然。
答李汝成(穲)问目
三岁前收养。若其亲叔侄。则似无报服三年之义。来教诚为正当。而古制及大典。有齐衰三年之文。但又有己之父母在。则降服期。心丧三年。若父殁长子。则期而除之文。故先辈多从服期心丧三年之制。盖亲子则杖期行禫。而收养服期者。无杖禫只心丧。此为有别。未知如何。
长房递迁之位改题与否。前辈议论不一。问解以为改题宜然。而愚伏以为不可改题。家礼但云告迁于祠堂。告毕迁于最长之房。其馀改题云云。则递迁位。似无改题之仪。且念人家当迁之长房既多。续续改题。亦似烦数未安耳。
礼。斩衰之丧。既虞卒哭。遭齐衰之丧。则着齐衰之带而兼包斩带云。况母丧心制则服已除矣。岂可以心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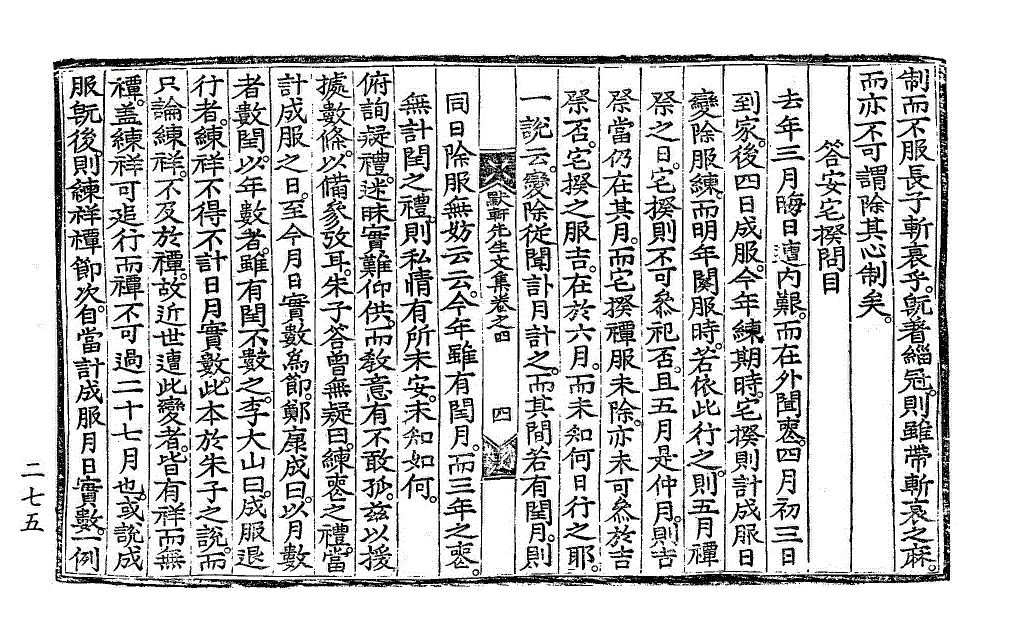 制而不服长子斩衰乎。既着缁冠。则虽带斩衰之麻。而亦不可谓除其心制矣。
制而不服长子斩衰乎。既着缁冠。则虽带斩衰之麻。而亦不可谓除其心制矣。答安宅揆问目
去年三月晦日遭内艰。而在外闻丧。四月初三日到家。后四日成服。今年练期时。宅揆则计成服日变除服练。而明年阕服时。若依此行之。则五月禫祭之日。宅揆则不可参祀否。且五月是仲月。则吉祭当仍在其月。而宅揆禫服未除。亦未可参于吉祭否。宅揆之服吉。在于六月。而未知何日行之耶。一说云。变除从闻讣月计之。而其间若有闰月。则同日除服无妨云云。今年虽有闰月。而三年之丧。无计闰之礼。则私情有所未安。未知如何。
俯询疑礼。迷昧实难仰供。而教意有不敢孤。玆以援据数条。以备参考耳。朱子答曾无疑曰。练丧之礼。当计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实数为节。郑康成曰。以月数者数闰。以年数者。虽有闰不数之。李大山曰。成服退行者。练祥不得不计日月实数。此本于朱子之说。而只论练祥。不及于禫。故近世遭此变者。皆有祥而无禫。盖练祥可追行而禫不可过二十七月也。或说成服既后。则练祥禫节次。自当计成服月日实数。一例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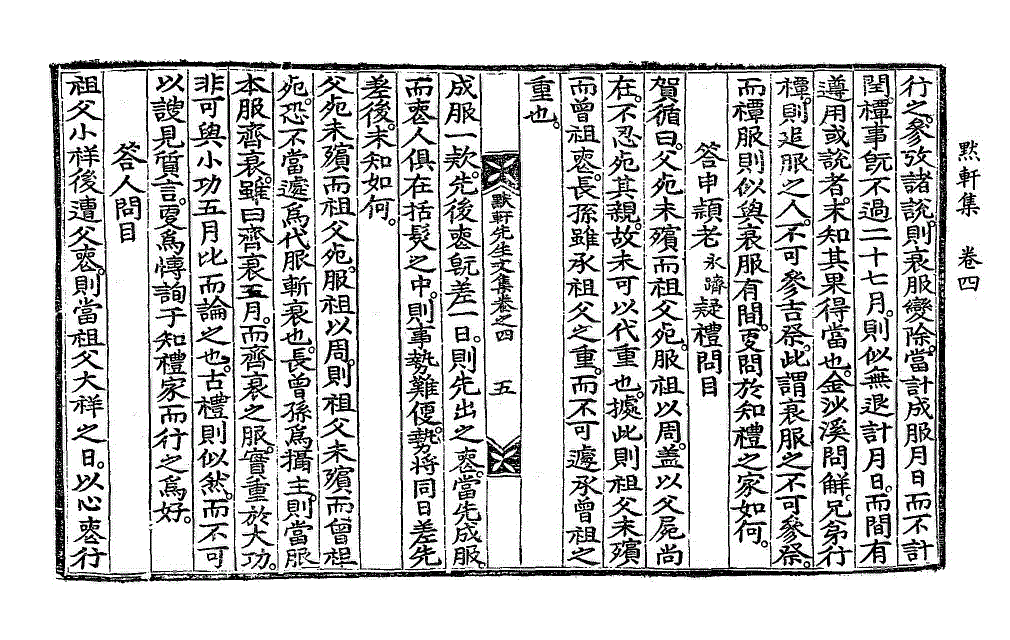 行之。参考诸说。则衰服变除。当计成服月日而不计闰。禫事既不过二十七月。则似无退计月日。而间有遵用或说者。未知其果得当也。金沙溪问解。兄弟行禫。则追服之人。不可参吉祭。此谓衰服之不可参祭。而禫服则似与衰服有间。更问于知礼之家如何。
行之。参考诸说。则衰服变除。当计成服月日而不计闰。禫事既不过二十七月。则似无退计月日。而间有遵用或说者。未知其果得当也。金沙溪问解。兄弟行禫。则追服之人。不可参吉祭。此谓衰服之不可参祭。而禫服则似与衰服有间。更问于知礼之家如何。答申颖老(永跻)疑礼问目
贺循曰。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盖以父尸尚在。不忍死其亲。故未可以代重也。据此则祖父未殡而曾祖丧。长孙虽承祖父之重。而不可遽承曾祖之重也。
成服一款。先后丧既差一日。则先出之丧。当先成服。而丧人俱在括发之中。则事势难便。势将同日差先差后。未知如何。
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则祖父未殡而曾祖死。恐不当遽为代服斩衰也。长曾孙为摄主。则当服本服齐衰。虽曰齐衰三月。而齐衰之服。实重于大功。非可与小功五月比而论之也。古礼则似然。而不可以謏见质言。更为博询于知礼家而行之为好。
答人问目
祖父小祥后遭父丧。则当祖父大祥之日。以心丧行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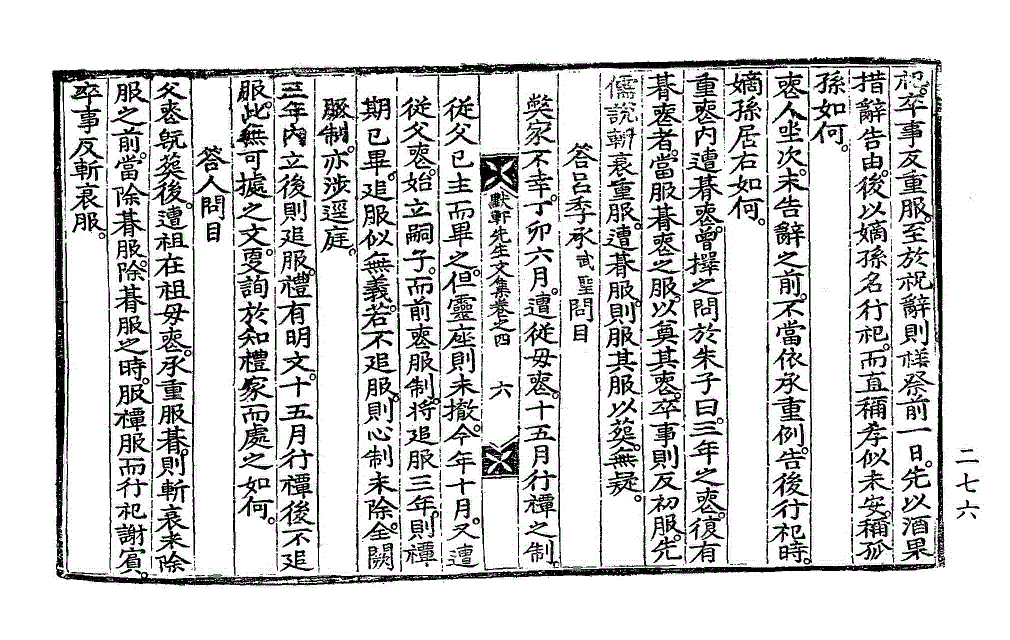 祀。卒事反重服。至于祝辞则祥祭前一日。先以酒果措辞告由。后以嫡孙名行祀。而直称孝似未安。称孤孙如何。
祀。卒事反重服。至于祝辞则祥祭前一日。先以酒果措辞告由。后以嫡孙名行祀。而直称孝似未安。称孤孙如何。丧人坐次。未告辞之前。不当依承重例。告后行祀时。嫡孙居右如何。
重丧内遭期丧。曾择之问于朱子曰。三年之丧。复有期丧者。当服期丧之服。以奠其丧。卒事则反初服。先儒说斩衰重服。遭期服。则服其服以葬。无疑。
答吕季承(武圣)问目
弊家不幸。丁卯六月。遭从母丧。十五月行禫之制。从父已主而毕之。但灵座则未撤。今年十月。又遭从父丧。始立嗣子。而前丧服制。将追服三年。则禫期已毕。追服似无义。若不追服。则心制未除。全阙服制。亦涉径庭。
三年内立后则追服。礼有明文。十五月行禫后不追服。此无可据之文。更询于知礼家而处之如何。
答人问目
父丧既葬后。遭祖在祖母丧。承重服期。则斩衰未除服之前。当除期服。除期服之时。服禫服而行祀谢宾。卒事反斩衰服。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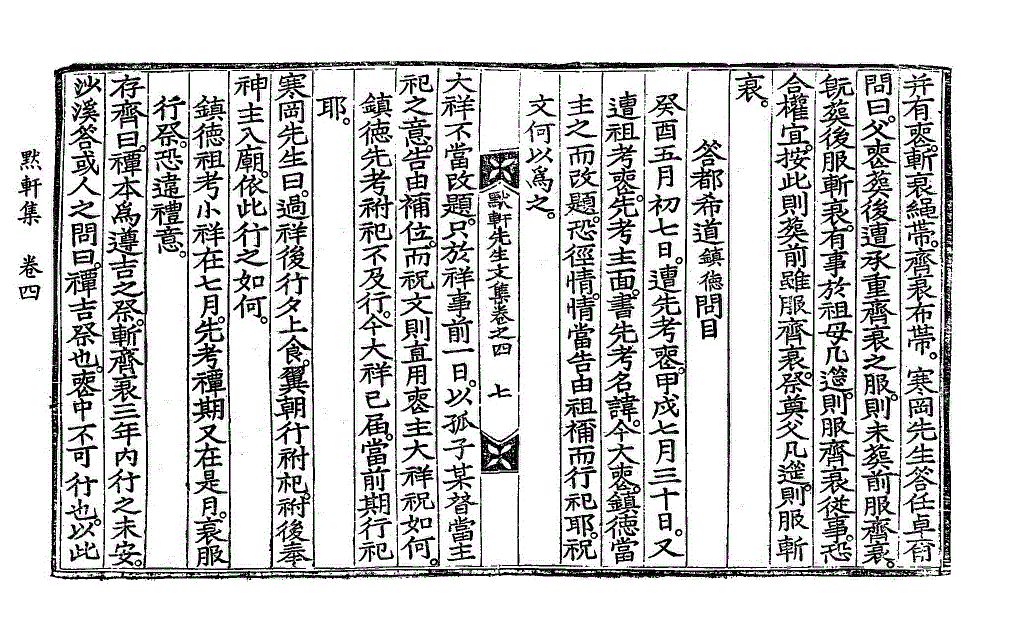 并有丧。斩衰绳带。齐衰布带。 寒冈先生答任卓尔问曰。父丧葬后遭承重齐衰之服。则未葬前服齐衰。既葬后服斩衰。有事于祖母几筵。则服齐衰从事。恐合权宜。按此则葬前虽服齐衰。祭奠父几筵。则服斩衰。
并有丧。斩衰绳带。齐衰布带。 寒冈先生答任卓尔问曰。父丧葬后遭承重齐衰之服。则未葬前服齐衰。既葬后服斩衰。有事于祖母几筵。则服齐衰从事。恐合权宜。按此则葬前虽服齐衰。祭奠父几筵。则服斩衰。答都希道(镇德)问目
癸酉五月初七日。遭先考丧。甲戌七月三十日。又遭祖考丧。先考主面。书先考名讳。今大丧。镇德当主之而改题。恐径情。情当告由祖祢而行祀耶。祝文何以为之。
大祥不当改题。只于祥事前一日。以孤子某替当主祀之意。告由祢位。而祝文则直用丧主大祥祝如何。
镇德先考祔祀不及行。今大祥已届。当前期行祀耶。
寒冈先生曰。过祥后行夕上食。翼朝行祔祀。祔后奉神主入庙。依此行之如何。
镇德祖考小祥在七月。先考禫期又在是月。衰服行祭。恐违礼意。
存齐曰。禫本为遵吉之祭。斩齐衰三年内行之未安。沙溪答或人之问曰。禫吉祭也。丧中不可行也。以此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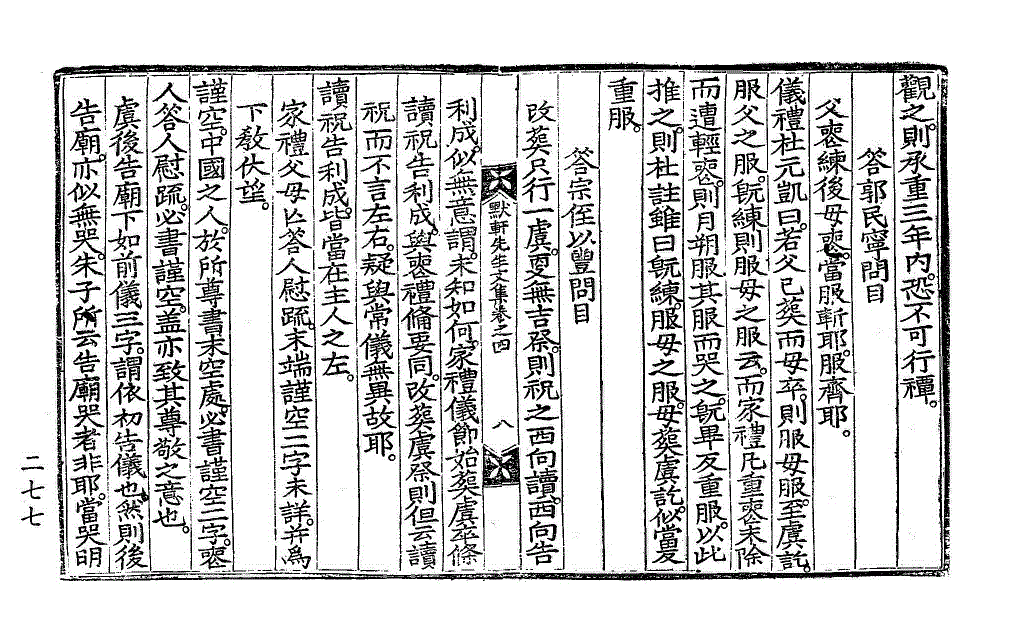 观之。则承重三年内。恐不可行禫。
观之。则承重三年内。恐不可行禫。答郭民宁问目
父丧练后母丧。当服斩耶。服齐耶。
仪礼杜元凯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则服母服。至虞讫。服父之服。既练则服母之服云。而家礼凡重丧未除而遭轻丧。则月朔服其服而哭之。既毕反重服。以此推之。则杜注虽曰既练。服母之服。母葬虞讫。似当反重服。
答宗侄以丰问目
改葬只行一虞。更无吉祭。则祝之西向读。西向告利成。似无意谓。未知如何。家礼仪节始葬虞卒条读祝告利成。与丧礼备要同。改葬虞祭则但云读祝而不言左右。疑与常仪无异故耶。
读祝告利成。皆当在主人之左。
家礼父母亡答人慰疏。末端谨空二字未详。并为下教伏望。
谨空。中国之人。于所尊书末空处。必书谨空二字。丧人答人慰疏。必书谨空。盖亦致其尊敬之意也。
虞后告庙下如前仪三字。谓依初告仪也。然则后告庙。亦似无哭。朱子所云告庙哭者非耶。当哭明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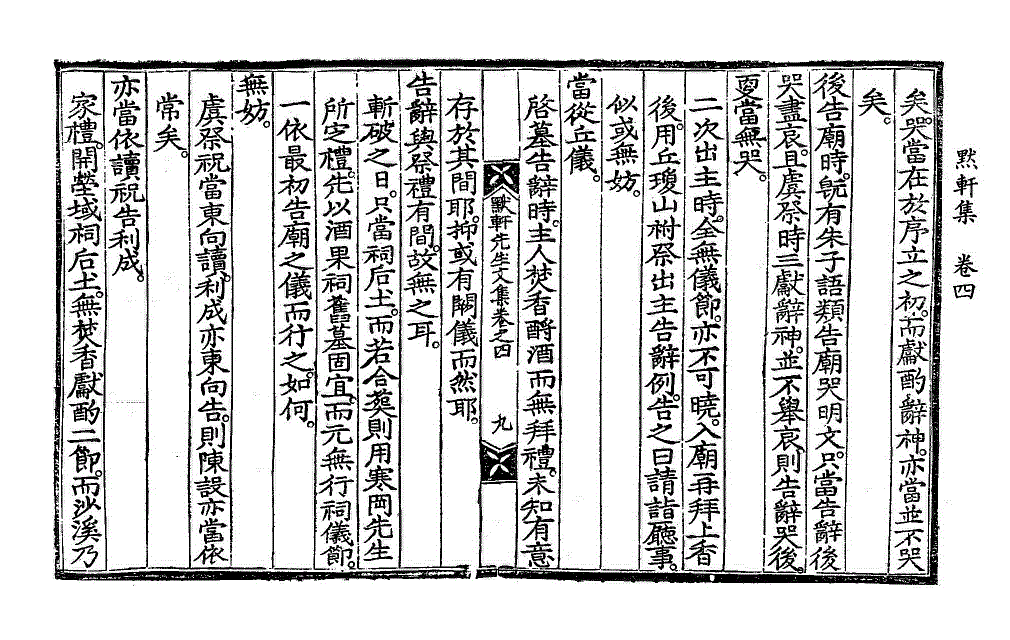 矣。哭当在于序立之初。而献酌辞神。亦当并不哭矣。
矣。哭当在于序立之初。而献酌辞神。亦当并不哭矣。后告庙时。既有朱子语类告庙哭明文。只当告辞后哭尽哀。且虞祭时三献辞神。并不举哀。则告辞哭后。更当无哭。
二次出主时。全无仪节。亦不可晓。入庙再拜上香后。用丘琼山祔祭出主告辞例。告之曰请诣厅事。似或无妨。
当从丘仪。
启墓告辞时。主人焚香酹酒而无拜礼。未知有意存于其间耶。抑或有阙仪而然耶。
告辞与祭礼有间。故无之耳。
斩破之日。只当祠后土。而若合葬则用寒冈先生所定礼。先以酒果祠旧墓固宜。而元无行祠仪节。一依最初告庙之仪而行之。如何。
无妨。
虞祭祝当东向读。利成亦东向告。则陈设亦当依常矣。
亦当依读祝告利成。
家礼。开茔域祠后土。无焚香献酌二节。而沙溪乃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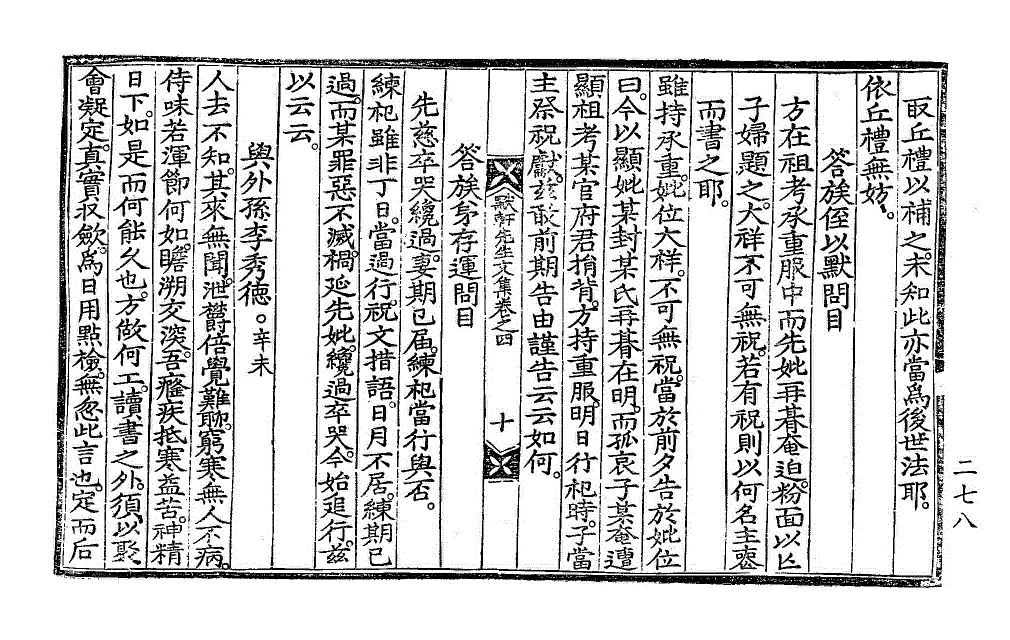 取丘礼以补之。未知此亦当为后世法耶。
取丘礼以补之。未知此亦当为后世法耶。依丘礼无妨。
答族侄以默问目
方在祖考承重服中而先妣再期奄迫。粉面以亡子妇题之。大祥不可无祝。若有祝则以何名主丧而书之耶。
虽持承重。妣位大祥。不可无祝。当于前夕告于妣位曰。今以显妣某封某氏再期在明。而孤哀子某奄遭显祖考某官府君捐背。方持重服。明日行祀时。子当主祭祝献。玆敢前期告由谨告云云如何。
答族弟存运问目
先慈卒哭才过。妻期已届。练祀当行与否。
练祀虽非丁日。当过行。祝文措语。日月不居。练期已过。而某罪恶不灭。祸延先妣。才过卒哭。今始追行。玆以云云。
与外孙李秀德(辛未)
人去不知。其来无闻。泄郁倍觉难聊。穷寒无人不病。侍味若浑节何如。瞻溯交深。吾癃疾抵寒益苦。神精日下。如是而何能久也。方做何工。读书之外。须以聚会凝定。真实收敛。为日用点检。无忽此言也。定而后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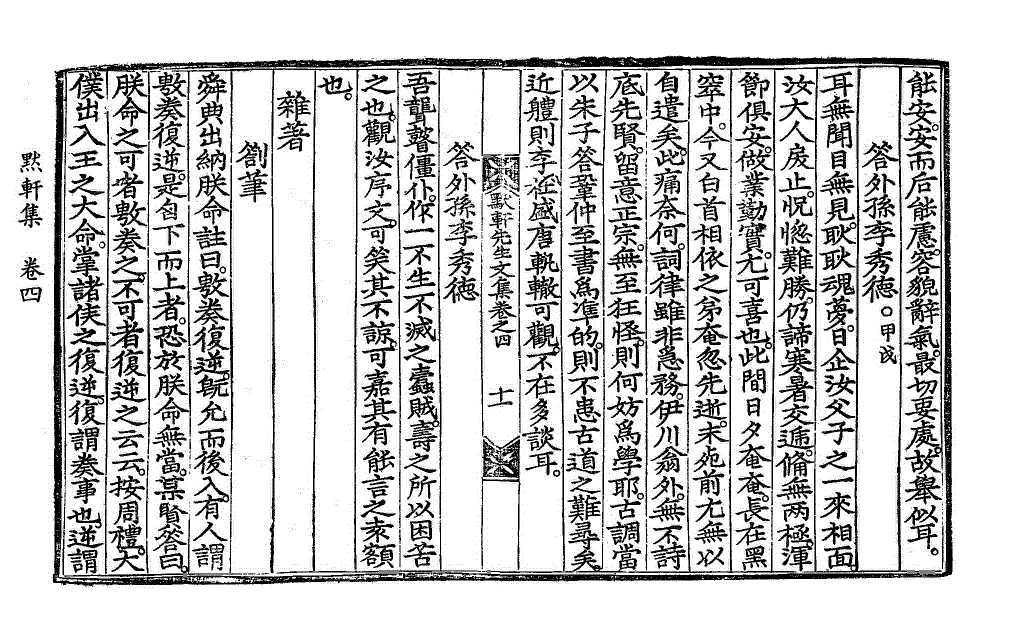 能安。安而后能虑。容貌辞气。最切要处。故举似耳。
能安。安而后能虑。容貌辞气。最切要处。故举似耳。答外孙李秀德(甲戌)
耳无闻目无见。耿耿魂梦。日企汝父子之一来相面。汝大人戾止。恍惚难胜。仍谛寒暑交递。备无两极。浑节俱安。做业勤实。尤可喜也。此间日夕奄奄。长在黑窣中。今又白首相依之弟奄忽先逝。未死前尤无以自遣矣。此痛奈何。词律虽非急务。伊川翁外。无不诗底先贤。留意正宗。无至狂怪。则何妨为学耶。古调当以朱子答巩仲至书为准的。则不患古道之难寻矣。近体则李杜盛唐轨辙可观。不在多谈耳。
答外孙李秀德
吾聋𥌒僵仆。作一不生不灭之蠹贼。寿之所以困苦之也。观汝序文。可笑其不谅。可嘉其有能言之袁额也。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杂著
劄笔
舜典出纳朕命注曰。敷奏复逆。既允而后入。有人谓敷奏复逆。是自下而上者。恐于朕命无当。某贤答曰。朕命之可者敷奏之。不可者复逆之云云。按周礼。大仆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复谓奏事也。逆谓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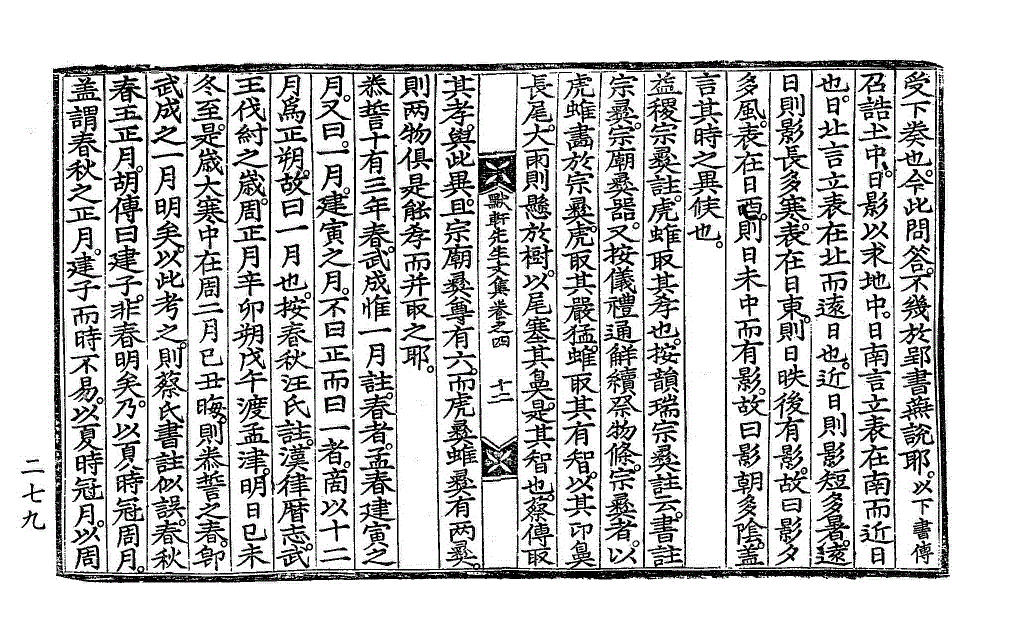 受下奏也。今此问答。不几于郢书燕说耶。(以下书传)
受下奏也。今此问答。不几于郢书燕说耶。(以下书传)召诰土中。日影以求地中。日南言立表在南而近日也。日北言立表在北而远日也。近日则影短多暑。远日则影长多寒。表在日东。则日昳后有影。故曰影夕多风。表在日西。则日未中而有影。故曰影朝多阴。盖言其时之异候也。
益稷宗彝注。虎蜼取其孝也。按韵瑞宗彝注云。书注宗彝。宗庙彝器。又按仪礼通解续祭物条。宗彝者。以虎蜼画于宗彝。虎取其严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长尾。大雨则悬于树。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蔡传取其孝。与此异。且宗庙彝尊有六。而虎彝虽彝有两彝。则两物俱是能孝而并取之耶。
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注。春者。孟春建寅之月。又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以十二月为正朔。故曰一月也。按春秋汪氏注。汉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卯朔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岁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则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以此考之。则蔡氏书注似误。春秋春王正月。胡传曰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盖谓春秋之正月。建子而时不易。以夏时冠月。以周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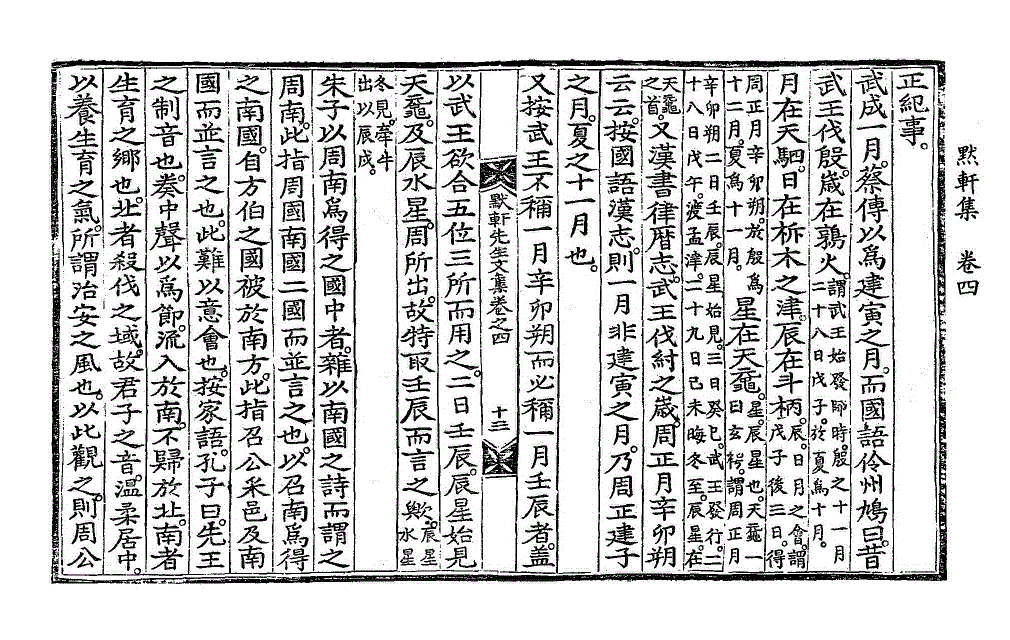 正纪事。
正纪事。武成一月。蔡传以为建寅之月。而国语伶州鸠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谓武王始发师时。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辰。日月之会。谓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为十二月。夏为十一月。)星在天鼋。(星。辰星也。天鼋一曰玄枵。谓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见。三日癸巳。武王发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天鼋之首。)又汉书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卯朔云云。按国语汉志。则一月非建寅之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也。
又按武王不称一月辛卯朔而必称一月壬辰者。盖以武王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二日壬辰。辰星始见天鼋。及辰水星。周所出。故特取壬辰而言之欤。(辰星水星冬见。牵牛出以辰戌。)
朱子以周南为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此指周国南国二国而并言之也。以召南为得之南国。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此指召公采邑及南国而并言之也。此难以意会也。按家语。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也。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所谓治安之风也。以此观之。则周公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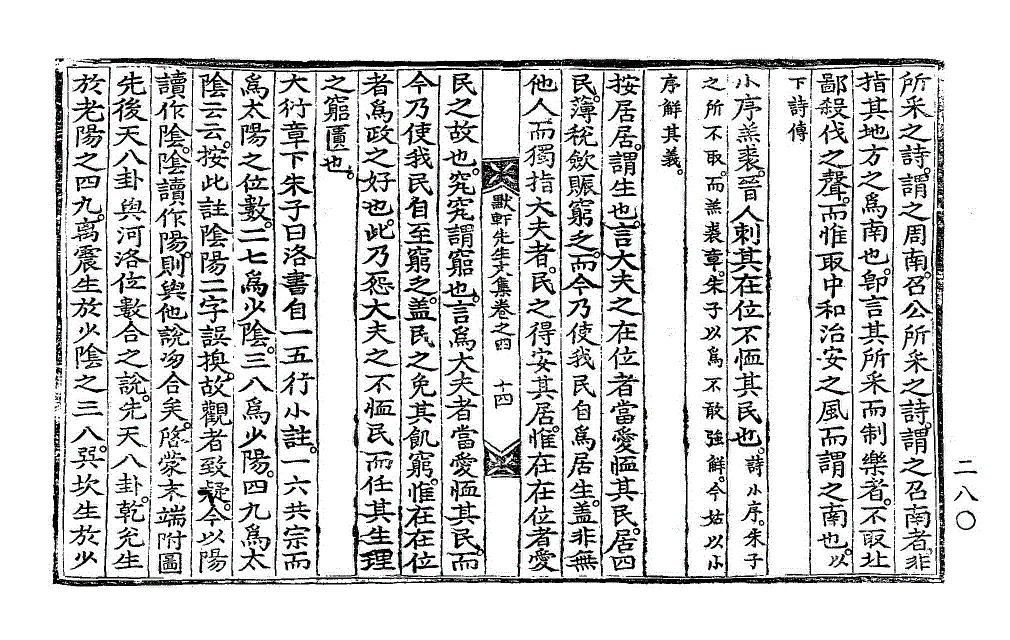 所采之诗。谓之周南。召公所采之诗。谓之召南者。非指其地方之为南也。即言其所采而制乐者。不取北鄙杀伐之声。而惟取中和治安之风而谓之南也。(以下诗传)
所采之诗。谓之周南。召公所采之诗。谓之召南者。非指其地方之为南也。即言其所采而制乐者。不取北鄙杀伐之声。而惟取中和治安之风而谓之南也。(以下诗传)小序羔裘。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诗小序。朱子之所不取。而羔裘章。朱子以为不敢强解。今姑以小序解其义。)
按居居。谓生也。言大夫之在位者当爱恤其民。居四民。薄税敛赈穷乏。而今乃使我民自为居生。盖非无他人而独指大夫者。民之得安其居。惟在在位者爱民之故也。究究谓穷也。言为大夫者当爱恤其民。而今乃使我民自至穷乏。盖民之免其饥穷。惟在在位者为政之好也。此乃怨大夫之不恤民而任其生理之穷匮也。
大衍章下朱子曰洛书自一五行小注。一六共宗而为太阳之位数。二七为少阴。三八为少阳。四九为太阴云云。按此注阴阳二字误换。故观者致疑。今以阳读作阴。阴读作阳。则与他说吻合矣。启蒙末端附图先后天八卦与河洛位数合之说。先天八卦。乾兑生于老阳之四九。离震生于少阴之三八。巽坎生于少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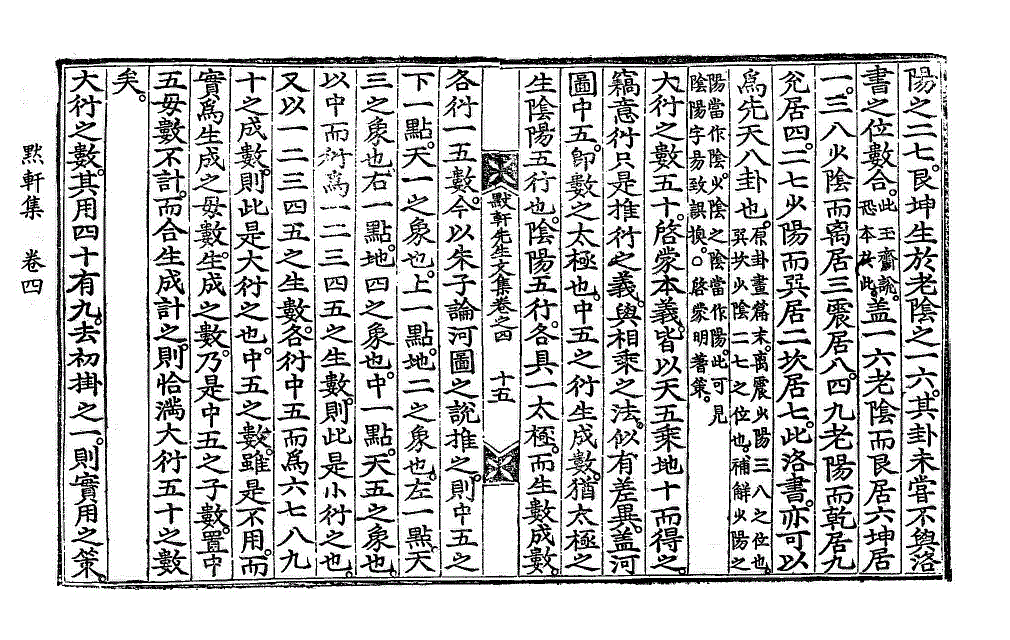 阳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阴之一六。其卦未尝不与洛书之位数合。(此玉斋说。恐本于此。)盖一六老阴而艮居六坤居一。三八少阴而离居三震居八。四九老阳而乾居九兑居四。二七少阳而巽居二坎居七。此洛书。亦可以为先天八卦也。(原卦画篇末。离震少阳三八之位也。巽坎少阴二七之位也。补解少阳之阳当作阴。少阴之阴当作阳。此可见阴阳字易致误换。○启蒙明蓍策。)
阳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阴之一六。其卦未尝不与洛书之位数合。(此玉斋说。恐本于此。)盖一六老阴而艮居六坤居一。三八少阴而离居三震居八。四九老阳而乾居九兑居四。二七少阳而巽居二坎居七。此洛书。亦可以为先天八卦也。(原卦画篇末。离震少阳三八之位也。巽坎少阴二七之位也。补解少阳之阳当作阴。少阴之阴当作阳。此可见阴阳字易致误换。○启蒙明蓍策。)大衍之数五十。启蒙本义。皆以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窃意衍只是推衍之义。与相乘之法。似有差异。盖河图中五。即数之太极也。中五之衍生成数。犹太极之生阴阳五行也。阴阳五行。各具一太极。而生数成数。各衍一五数。今以朱子论河图之说推之。则中五之下一点。天一之象也。上一点。地二之象也。左一点。天三之象也。右一点。地四之象也。中一点。天五之象也。以中而衍为一二三四五之生数。则此是小衍之也。又以一二三四五之生数。各衍中五而为六七八九十之成数。则此是大衍之也。中五之数。虽是不用。而实为生成之母数。生成之数。乃是中五之子数。置中五母数不计。而合生成计之。则恰满大衍五十之数矣。
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去初挂之一。则实用之策。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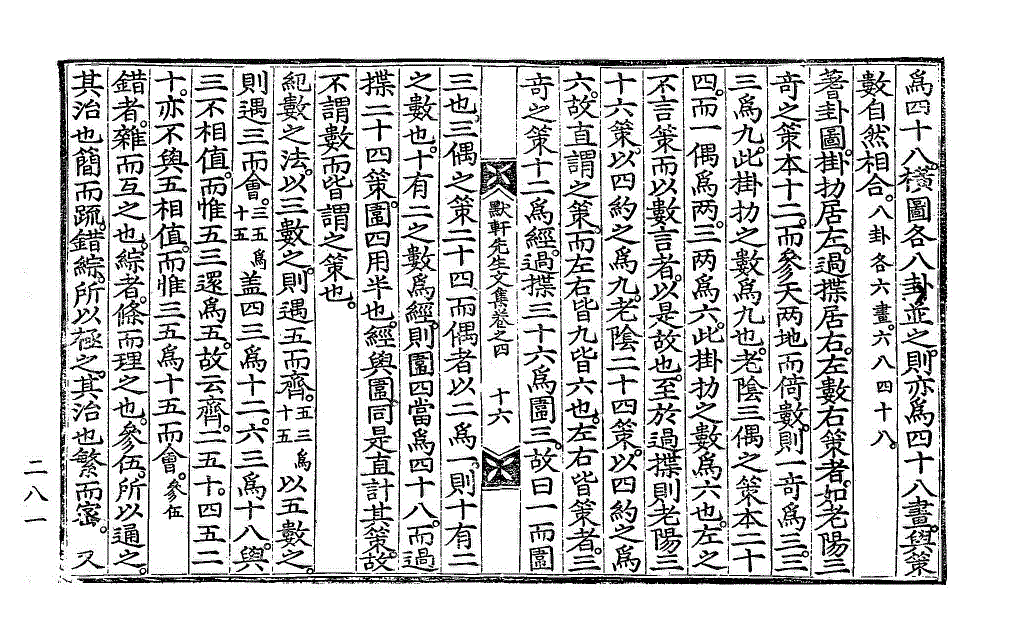 为四十八。横图各八卦并之。则亦为四十八画。与策数自然相合。(八卦各六画。六八四十八。)
为四十八。横图各八卦并之。则亦为四十八画。与策数自然相合。(八卦各六画。六八四十八。)蓍卦图。挂扐居左。过揲居右。左数右策者。如老阳三奇之策本十二。而参天两地而倚数。则一奇为三。三三为九。此挂扐之数为九也。老阴三偶之策本二十四。而一偶为两。三两为六。此挂扐之数为六也。左之不言策而以数言者。以是故也。至于过揲则老阳三十六策。以四约之为九。老阴二十四策。以四约之为六。故直谓之策。而左右皆九皆六也。左右皆策者。三奇之策十二为经。过揲三十六为围三。故曰一而围三也。三偶之策二十四。而偶者以二为一。则十有二之数也。十有二之数为经。则围四当为四十八。而过揲二十四策。围四用半也。经与围。同是直计其策。故不谓数而皆谓之策也。
纪数之法。以三数之。则遇五而齐。(五三为十五。)以五数之。则遇三而会。(三五为十五。)盖四三为十二。六三为十八。与三不相值。而惟五三还为五。故云齐。二五十。四五二十。亦不与五相值。而惟三五为十五而会。(参伍。)
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也繁而密。 又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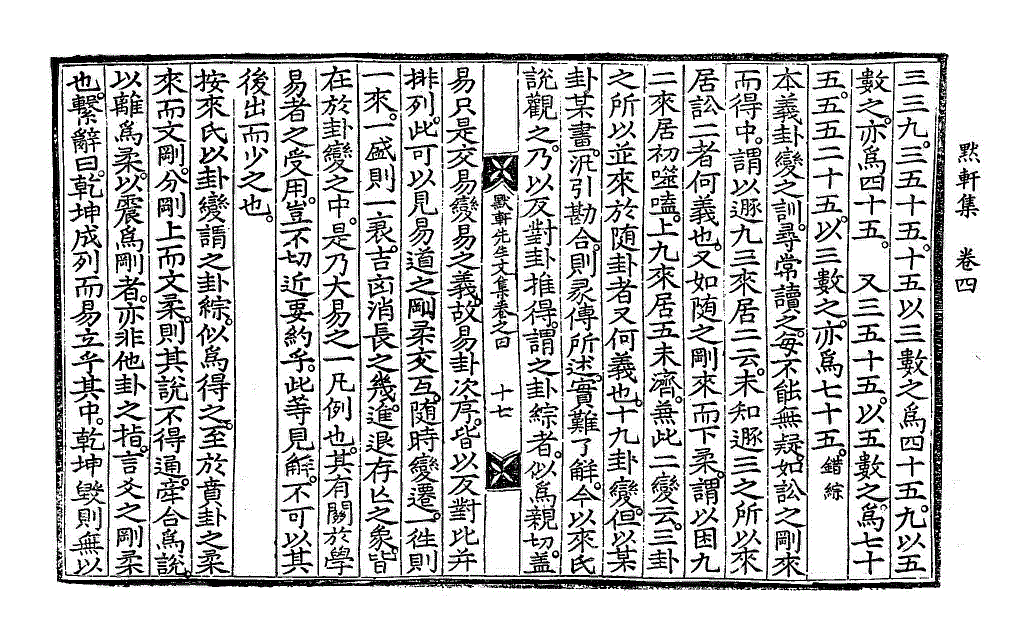 三三九。三五十五。十五以三数之为四十五。九以五数之。亦为四十五。 又三五十五。以五数之。为七十五。五五二十五。以三数之。亦为七十五。(错综。)
三三九。三五十五。十五以三数之为四十五。九以五数之。亦为四十五。 又三五十五。以五数之。为七十五。五五二十五。以三数之。亦为七十五。(错综。)本义卦变之训。寻常读之。每不能无疑。如讼之刚来而得中。谓以遁九三来居二云。未知遁三之所以来居讼二者何义也。又如随之刚来而下柔。谓以困九二来居初噬嗑。上九来居五未济。兼此二变云。三卦之所以并来于随卦者又何义也。十九卦变。但以某卦某画。汎引勘合。则彖传所述。实难了解。今以来氏说观之。乃以反对卦推得。谓之卦综者。似为亲切。盖易只是交易变易之义。故易卦次序。皆以反对比并排列。此可以见易道之刚柔交互。随时变迁。一往则一来。一盛则一衰。吉凶消长之几。进退存亡之象。皆在于卦变之中。是乃大易之一凡例也。其有关于学易者之受用。岂不切近要约乎。此等见解。不可以其后出而少之也。
按来氏以卦变谓之卦综。似为得之。至于贲卦之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则其说不得通。牵合为说。以离为柔。以震为刚者。亦非他卦之指。言爻之刚柔也。系辞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则无以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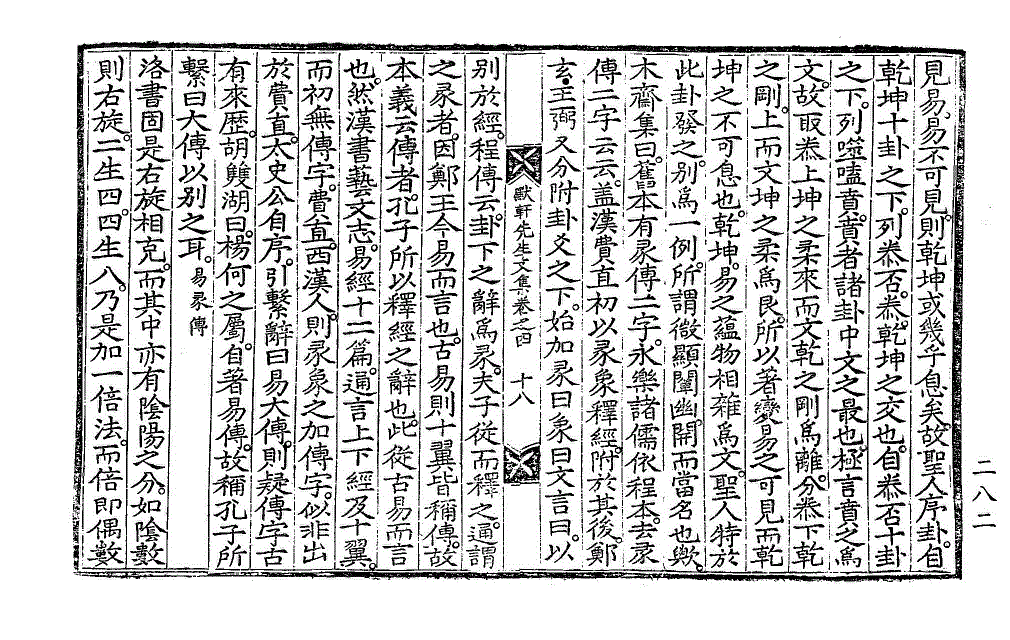 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故圣人序卦。自乾坤十卦之下。列泰否。泰。乾坤之交也。自泰否十卦之下。列噬嗑贲。贲者诸卦中文之最也。极言贲之为文。故取泰上坤之柔来而文乾之刚为离。分泰下乾之刚。上而文坤之柔为艮。所以著变易之可见而乾坤之不可息也。乾坤。易之蕴物相杂为文。圣人特于此卦发之。别为一例。所谓微显阐幽。开而当名也欤。木斋集曰。旧本有彖传二字。永乐诸儒依程本。去彖传二字云云。盖汉费直初以彖象释经。附于其后。郑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于经。程传云。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者。因郑王今易而言也。古易则十翼皆称传。故本义云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此从古易而言也。然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通言上下经及十翼。而初无传字。费直。西汉人。则彖象之加传字。似非出于费直。太史公自序。引系辞曰易大传。则疑传字古有来历。胡双湖曰。杨何之属。自著易传。故称孔子所系曰大传以别之耳。(易彖传)
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故圣人序卦。自乾坤十卦之下。列泰否。泰。乾坤之交也。自泰否十卦之下。列噬嗑贲。贲者诸卦中文之最也。极言贲之为文。故取泰上坤之柔来而文乾之刚为离。分泰下乾之刚。上而文坤之柔为艮。所以著变易之可见而乾坤之不可息也。乾坤。易之蕴物相杂为文。圣人特于此卦发之。别为一例。所谓微显阐幽。开而当名也欤。木斋集曰。旧本有彖传二字。永乐诸儒依程本。去彖传二字云云。盖汉费直初以彖象释经。附于其后。郑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于经。程传云。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者。因郑王今易而言也。古易则十翼皆称传。故本义云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此从古易而言也。然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通言上下经及十翼。而初无传字。费直。西汉人。则彖象之加传字。似非出于费直。太史公自序。引系辞曰易大传。则疑传字古有来历。胡双湖曰。杨何之属。自著易传。故称孔子所系曰大传以别之耳。(易彖传)洛书固是右旋相克。而其中亦有阴阳之分。如阴数则右旋。二生四。四生八。乃是加一倍法。而倍即偶数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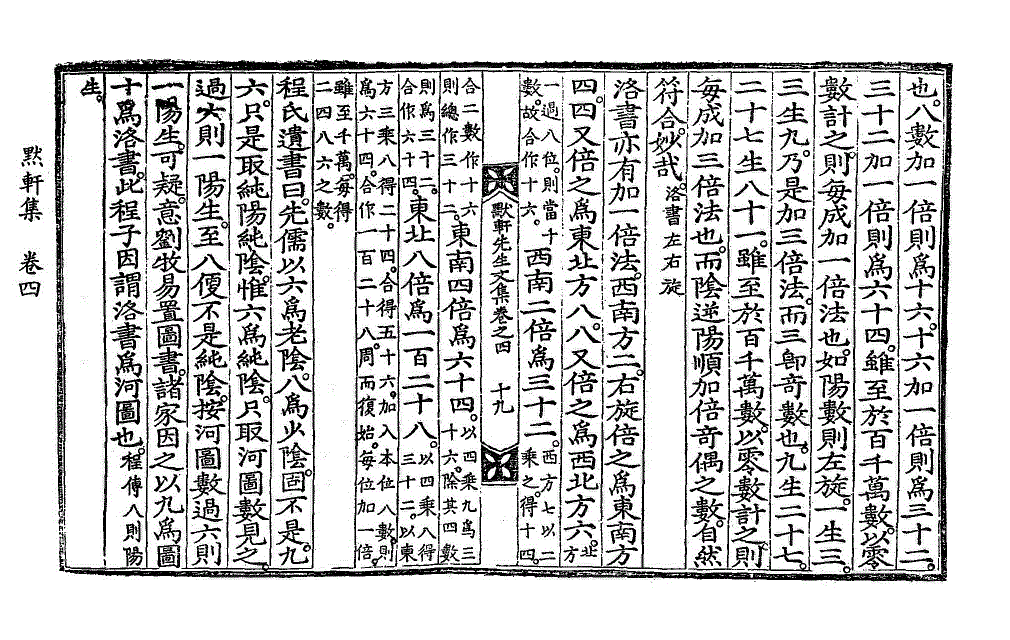 也。八数加一倍则为十六。十六加一倍则为三十二。三十二加一倍则为六十四。虽至于百千万数。以零数计之。则每成加一倍法也。如阳数则左旋。一生三。三生九。乃是加三倍法。而三即奇数也。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虽至于百千万数。以零数计之。则每成加三倍法也。而阴逆阳顺加倍奇偶之数。自然符合。妙哉。(洛书左右旋)
也。八数加一倍则为十六。十六加一倍则为三十二。三十二加一倍则为六十四。虽至于百千万数。以零数计之。则每成加一倍法也。如阳数则左旋。一生三。三生九。乃是加三倍法。而三即奇数也。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虽至于百千万数。以零数计之。则每成加三倍法也。而阴逆阳顺加倍奇偶之数。自然符合。妙哉。(洛书左右旋)洛书亦有加一倍法。西南方二。右旋倍之为东南方四。四又倍之为东北方八。八又倍之为西北方六。(北方一过八位。则当十数。故合作十六。)西南二倍为三十二。(西方七以二乘之。得十四。合二数作十六则总作三十二。)东南四倍为六十四。(以四乘九为三十六。除其四数则为三十二。合作六十四。)东北八倍为一百二十八。(以四乘八得三十二。以东方三乘八得二十四。合得五十六。加入本位八数。则为六十四。合作一百二十八。周而复始。每位加一倍。虽至千万。每得二四八六之数。)
程氏遗书曰。先儒以六为老阴。八为少阴。固不是。九六。只是取纯阳纯阴。惟六为纯阴。只取河图数见之。过六则一阳生。至八便不是纯阴。按河图数过六则一阳生。可疑。意刘牧易置图书。诸家因之以九为图十为洛书。此程子因谓洛书为河图也。(程传八则阳生)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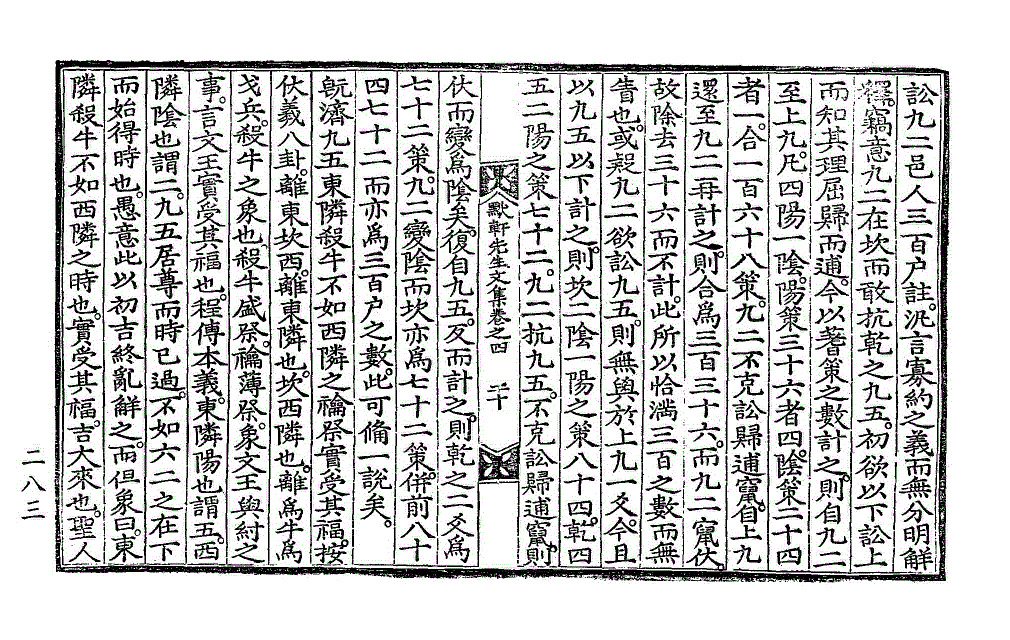 讼九二邑人三百户注。汎言寡约之义而无分明解释。窃意九二在坎而敢抗乾之九五。初欲以下讼上而知其理屈归而逋。今以蓍策之数计之。则自九二至上九。凡四阳一阴。阳策三十六者四。阴策二十四者一。合一百六十八策。九二不克讼归逋窜。自上九还至九二再计之。则合为三百三十六。而九二窜伏。故除去三十六而不计。此所以恰满三百之数而无眚也。或疑九二欲讼九五。则无与于上九一爻。今且以九五以下计之。则坎二阴一阳之策八十四。乾四五二阳之策七十二。九二抗九五。不克讼归逋窜。则伏而变为阴矣。复自九五。反而计之。则乾之二爻为七十二策。九二变阴而坎亦为七十二策。并前八十四七十二而亦为三百户之数。此可备一说矣。
讼九二邑人三百户注。汎言寡约之义而无分明解释。窃意九二在坎而敢抗乾之九五。初欲以下讼上而知其理屈归而逋。今以蓍策之数计之。则自九二至上九。凡四阳一阴。阳策三十六者四。阴策二十四者一。合一百六十八策。九二不克讼归逋窜。自上九还至九二再计之。则合为三百三十六。而九二窜伏。故除去三十六而不计。此所以恰满三百之数而无眚也。或疑九二欲讼九五。则无与于上九一爻。今且以九五以下计之。则坎二阴一阳之策八十四。乾四五二阳之策七十二。九二抗九五。不克讼归逋窜。则伏而变为阴矣。复自九五。反而计之。则乾之二爻为七十二策。九二变阴而坎亦为七十二策。并前八十四七十二而亦为三百户之数。此可备一说矣。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按伏羲八卦。离东坎西。离东邻也。坎西邻也。离为牛为戈兵。杀牛之象也。杀牛盛祭。礿薄祭。象文王与纣之事。言文王实受其福也。程传本义。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愚意此以初吉终乱解之。而但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圣人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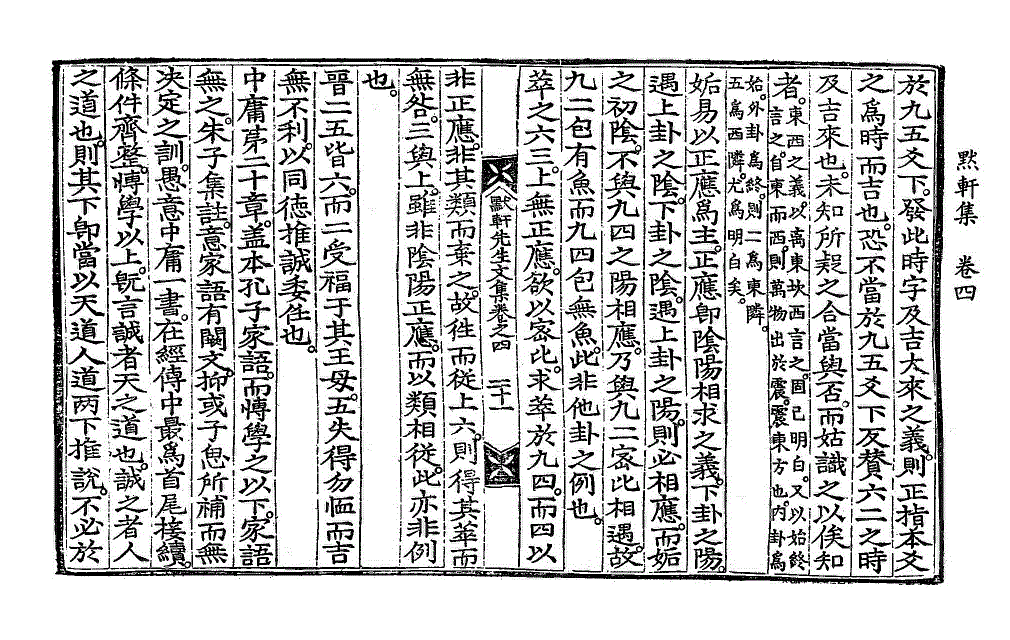 于九五爻下。发此时字及吉大来之义。则正指本爻之为时而吉也。恐不当于九五爻下反赞六二之时及吉来也。未知所疑之合当与否。而姑识之以俟知者。(东西之义。以离东坎西言之。固已明白。又以始终言之。自东而西。则万物出于震。震东方也。内卦为始。外卦为终。则二为东邻。五为西邻。尤为明白矣。)
于九五爻下。发此时字及吉大来之义。则正指本爻之为时而吉也。恐不当于九五爻下反赞六二之时及吉来也。未知所疑之合当与否。而姑识之以俟知者。(东西之义。以离东坎西言之。固已明白。又以始终言之。自东而西。则万物出于震。震东方也。内卦为始。外卦为终。则二为东邻。五为西邻。尤为明白矣。)姤易以正应为主。正应即阴阳相求之义。下卦之阳。遇上卦之阴。下卦之阴。遇上卦之阳。则必相应。而姤之初阴。不与九四之阳相应。乃与九二密比相遇。故九二包有鱼而九四包无鱼。此非他卦之例也。
萃之六三。上无正应。欲以密比。求萃于九四。而四以非正应。非其类而弃之。故往而从上六。则得其萃而无咎。三与上。虽非阴阳正应。而以类相从。此亦非例也。
晋二五皆六。而二受福于其王母。五失得勿恤而吉无不利。以同德推诚委任也。
中庸第二十章。盖本孔子家语。而博学之以下。家语无之。朱子集注。意家语有阙文。抑或子思所补而无决定之训。愚意中庸一书。在经传中最为首尾接续。条件齐整。博学以上。既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则其下即当以天道人道两下推说。不必于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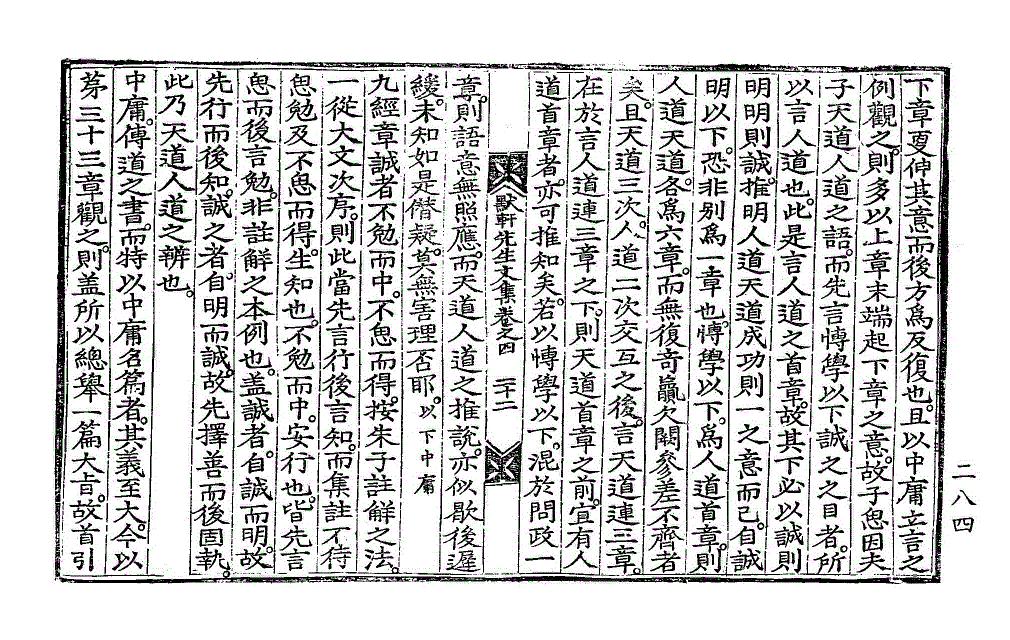 下章更伸其意而后方为反复也。且以中庸立言之例观之。则多以上章末端起下章之意。故子思因夫子天道人道之语。而先言博学以下诚之之目者。所以言人道也。此是言人道之首章。故其下必以诚则明明则诚。推明人道天道成功则一之意而已。自诚明以下。恐非别为一章也。博学以下。为人道首章。则人道天道。各为六章。而无复奇赢欠阙参差不齐者矣。且天道三次。人道二次交互之后。言天道连三章。在于言人道连三章之下。则天道首章之前。宜有人道首章者。亦可推知矣。若以博学以下。混于问政一章。则语意无照应。而天道人道之推说。亦似歇后迟缓。未知如是僭疑。莫无害理否耶。(以下中庸)
下章更伸其意而后方为反复也。且以中庸立言之例观之。则多以上章末端起下章之意。故子思因夫子天道人道之语。而先言博学以下诚之之目者。所以言人道也。此是言人道之首章。故其下必以诚则明明则诚。推明人道天道成功则一之意而已。自诚明以下。恐非别为一章也。博学以下。为人道首章。则人道天道。各为六章。而无复奇赢欠阙参差不齐者矣。且天道三次。人道二次交互之后。言天道连三章。在于言人道连三章之下。则天道首章之前。宜有人道首章者。亦可推知矣。若以博学以下。混于问政一章。则语意无照应。而天道人道之推说。亦似歇后迟缓。未知如是僭疑。莫无害理否耶。(以下中庸)九经章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按朱子注解之法。一从大文次序。则此当先言行后言知。而集注不待思勉及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皆先言思而后言勉。非注解之本例也。盖诚者。自诚而明。故先行而后知。诚之者。自明而诚。故先择善而后固执。此乃天道人道之辨也。
中庸。传道之书。而特以中庸名篇者。其义至大。今以第三十三章观之。则盖所以总举一篇大旨。故首引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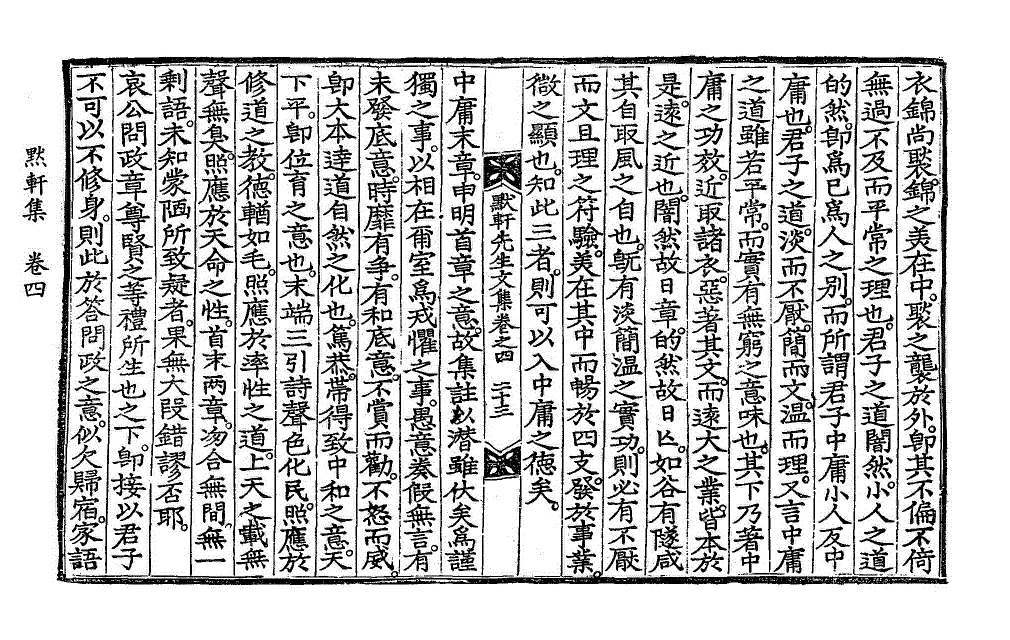 衣锦尚褧。锦之美在中。褧之袭于外。即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也。君子之道闇然。小人之道的然。即为己为人之别。而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又言中庸之道虽若平常。而实有无穷之意味也。其下乃著中庸之功效。近取诸衣。恶著其文。而远大之业。皆本于是。远之近也。闇然故日章。的然故日亡。如谷有隧咸其自取风之自也。既有淡简温之实功。则必有不厌而文且理之符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微之显也。知此三者。则可以入中庸之德矣。
衣锦尚褧。锦之美在中。褧之袭于外。即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也。君子之道闇然。小人之道的然。即为己为人之别。而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又言中庸之道虽若平常。而实有无穷之意味也。其下乃著中庸之功效。近取诸衣。恶著其文。而远大之业。皆本于是。远之近也。闇然故日章。的然故日亡。如谷有隧咸其自取风之自也。既有淡简温之实功。则必有不厌而文且理之符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微之显也。知此三者。则可以入中庸之德矣。中庸末章。申明首章之意。故集注以潜虽伏矣为谨独之事。以相在尔室为戒惧之事。愚意奏假无言。有未发底意。时靡有争。有和底意。不赏而劝。不怒而威。即大本达道自然之化也。笃恭。带得致中和之意。天下平。即位育之意也。末端三引诗声色化民。照应于修道之教。德輶如毛。照应于率性之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照应于天命之性。首末两章。吻合无间。无一剩语。未知蒙陋所致疑者。果无大段错谬否耶。
哀公问政章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之下。即接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则此于答问政之意。似欠归宿。家语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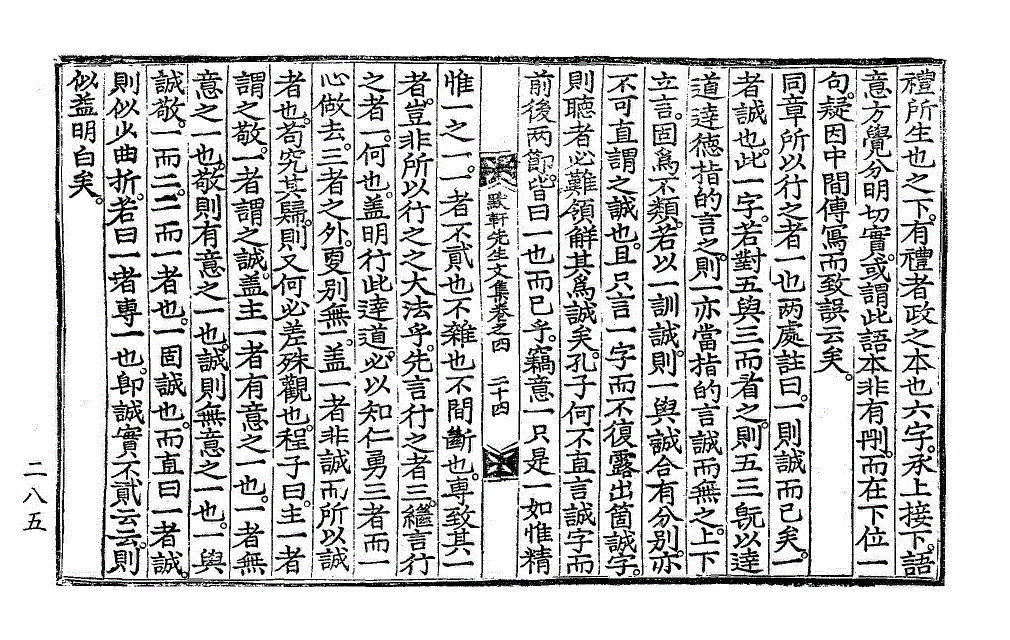 礼所生也之下。有礼者政之本也六字。承上接下。语意方觉分明切实。或谓此语本非有删。而在下位一句。疑因中间传写而致误云矣。
礼所生也之下。有礼者政之本也六字。承上接下。语意方觉分明切实。或谓此语本非有删。而在下位一句。疑因中间传写而致误云矣。同章所以行之者一也两处注曰。一则诚而已矣。一者诚也。此一字。若对五与三而看之。则五三既以达道达德指的言之。则一亦当指的言诚而无之。上下立言。固为不类。若以一训诚。则一与诚合有分别。亦不可直谓之诚也。且只言一字而不复露出个诚字。则听者必难领解其为诚矣。孔子何不直言诚字而前后两节。皆曰一也而已乎。窃意一只是一如惟精惟一之一。一者不贰也不杂也不间断也。专致其一者。岂非所以行之之大法乎。先言行之者三。继言行之者一。何也。盖明行此达道。必以知仁勇三者而一心做去。三者之外。更别无一。盖一者非诚而所以诚者也。苟究其归。则又何必差殊观也。程子曰。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盖主一者有意之一也。一者无意之一也。敬则有意之一也。诚则无意之一也。一与诚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一固诚也。而直曰一者诚。则似少曲折。若曰一者专一也。即诚实不贰云云。则似益明白矣。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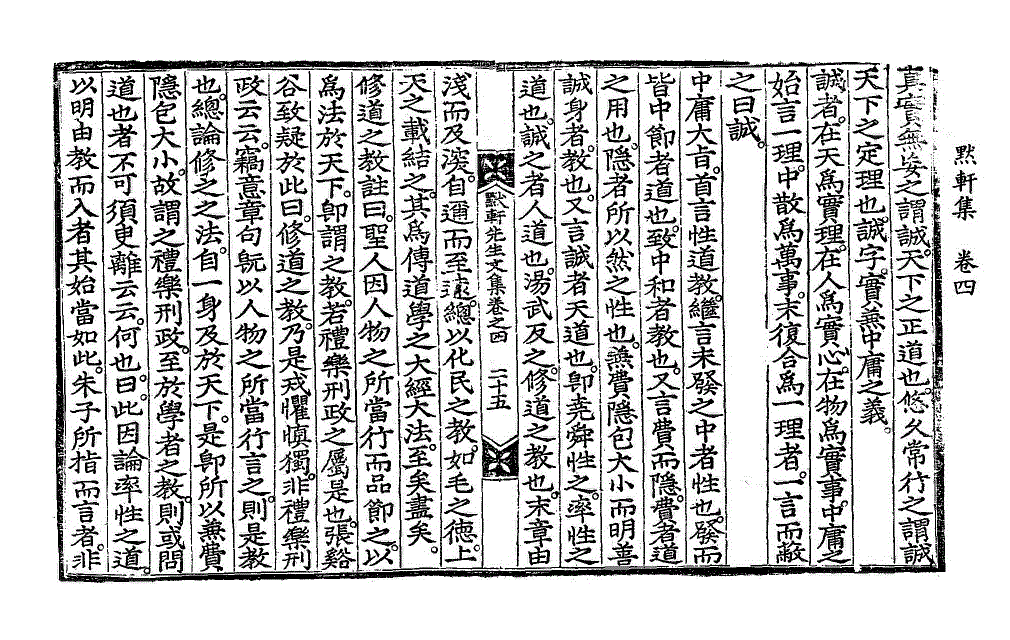 真实无妄之谓诚。天下之正道也。悠久常行之谓诚天下之定理也。诚字。实兼中庸之义。
真实无妄之谓诚。天下之正道也。悠久常行之谓诚天下之定理也。诚字。实兼中庸之义。诚者。在天为实理。在人为实心。在物为实事。中庸之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者。一言而蔽之曰诚。
中庸大旨。首言性道教。继言未发之中者性也。发而皆中节者道也。致中和者教也。又言费而隐。费者道之用也。隐者所以然之性也。兼费隐包大小而明善诚身者。教也。又言诚者天道也。即尧舜性之。率性之道也。诚之者人道也。汤武反之。修道之教也。末章由浅而及深。自迩而至远。总以化民之教。如毛之德。上天之载结之。其为传道学之大经大法。至矣尽矣。
修道之教注曰。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即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张溪谷致疑于此曰。修道之教。乃是戒惧慎独。非礼乐刑政云云。窃意章句既以人物之所当行言之。则是教也。总论修之之法。自一身及于天下。是即所以兼费隐包大小。故谓之礼乐刑政。至于学者之教。则或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云云。何也。曰。此因论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当如此。朱子所指而言者。非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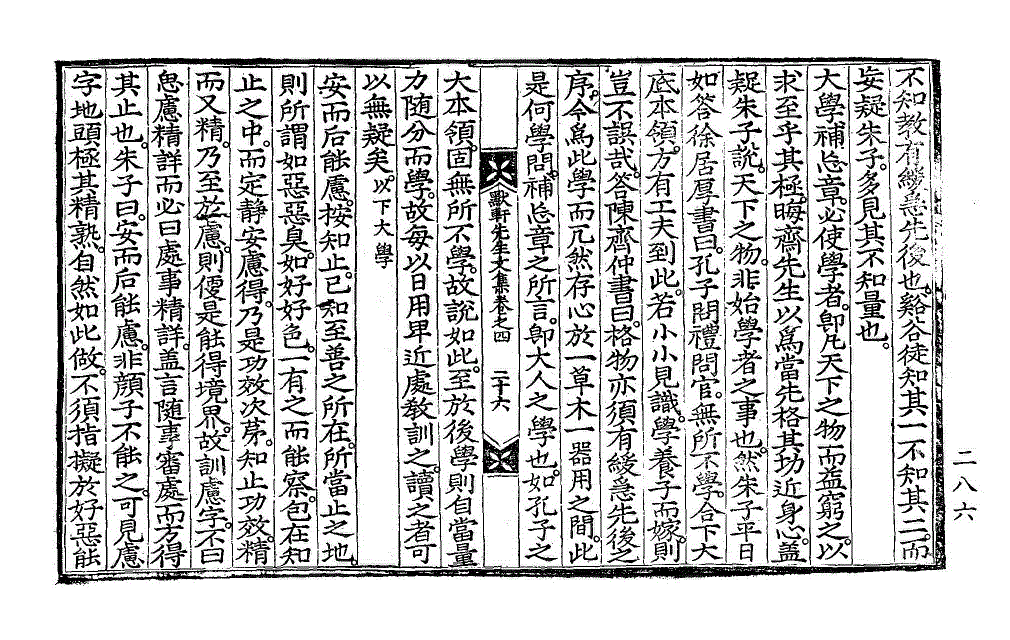 不知教有缓急先后也。溪谷徒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妄疑朱子。多见其不知量也。
不知教有缓急先后也。溪谷徒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妄疑朱子。多见其不知量也。大学补忘章。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晦斋先生以为当先格其切近身心。盖疑朱子说。天下之物。非始学者之事也。然朱子平日如答徐居厚书曰。孔子问礼问官。无所不学。合下大底本领。方有工夫到此。若小小见识。学养子而嫁。则岂不误哉。答陈齐仲书曰。格物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今为此学而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补忘章之所言。即大人之学也。如孔子之大本领。固无所不学。故说如此。至于后学则自当量力随分而学。故每以日用卑近处教训之。读之者可以无疑矣。(以下大学)
安而后能虑。按知止。已知至善之所在。所当止之地。则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有之而能察。包在知止之中。而定静安虑得。乃是功效次第。知止功效。精而又精。乃至于虑。则便是能得境界。故训虑字。不曰思虑精详而必曰处事精详。盖言随事审处而方得其止也。朱子曰。安而后能虑。非颜子不能之。可见虑字地头极其精熟。自然如此做。不须指拟于好恶能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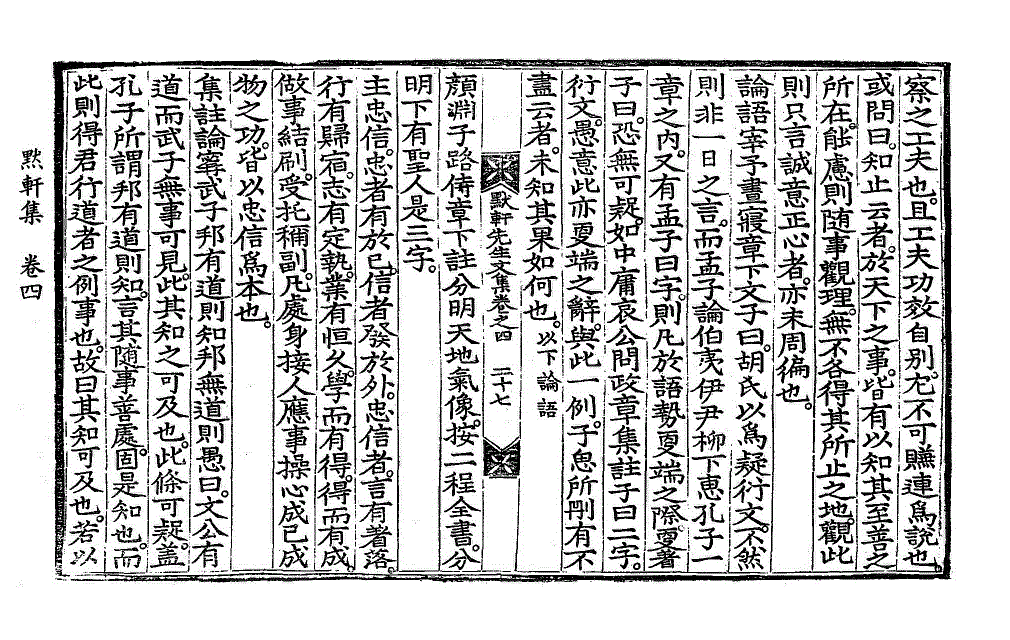 察之工夫也。且工夫功效自别。尤不可赚连为说也。或问曰。知止云者。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能虑则随事观理。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观此则只言诚意正心者。亦未周遍也。
察之工夫也。且工夫功效自别。尤不可赚连为说也。或问曰。知止云者。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能虑则随事观理。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观此则只言诚意正心者。亦未周遍也。论语宰予昼寝章下文子曰。胡氏以为疑衍文。不然则非一日之言。而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一章之内。又有孟子曰字。则凡于语势更端之际。更着子曰。恐无可疑。如中庸哀公问政章集注子曰二字。衍文。愚意此亦更端之辞。与此一例。子思所删有不尽云者。未知其果如何也。(以下论语)
颜渊子路侍章下注分明天地气像。按二程全书。分明下有圣人是三字。
主忠信。忠者有于己。信者发于外。忠信者。言有着落。行有归宿。志有定执。业有恒久。学而有得。得而有成。做事结刷。受托称副。凡处身接人应事操心成己成物之功。皆以忠信为本也。
集注论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曰。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此条可疑。盖孔子所谓邦有道则知。言其随事善处。固是知也。而此则得君行道者之例事也。故曰其知可及也。若以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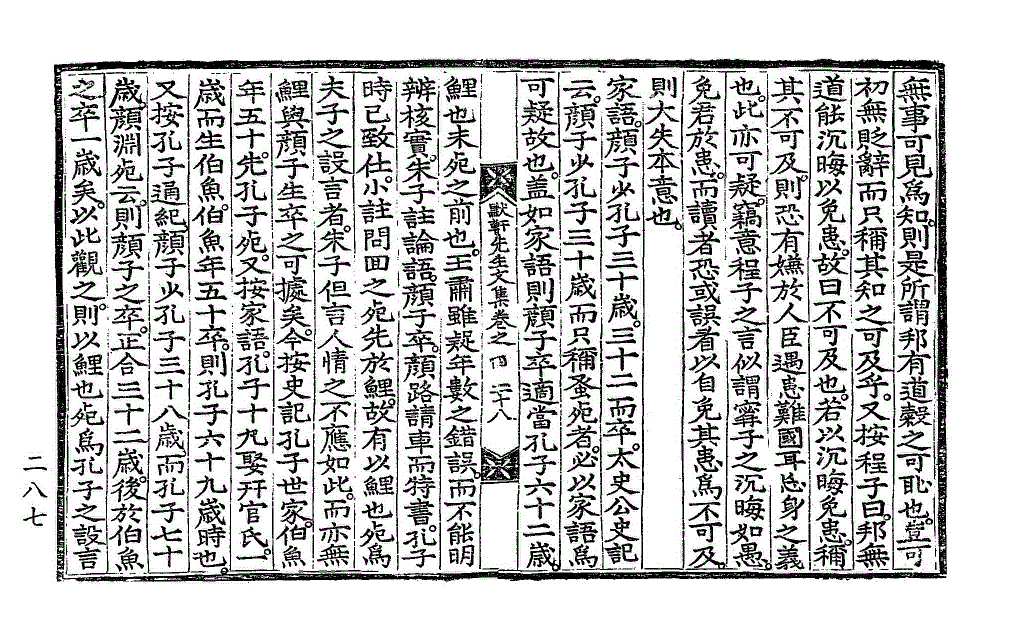 无事可见为知。则是所谓邦有道谷之可耻也。岂可初无贬辞而只称其知之可及乎。又按程子曰。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若以沉晦免患。称其不可及。则恐有嫌于人臣遇患难国耳忘身之义也。此亦可疑。窃意程子之言似谓宁子之沉晦如愚。免君于患。而读者恐或误看以自免其患为不可及。则大失本意也。
无事可见为知。则是所谓邦有道谷之可耻也。岂可初无贬辞而只称其知之可及乎。又按程子曰。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若以沉晦免患。称其不可及。则恐有嫌于人臣遇患难国耳忘身之义也。此亦可疑。窃意程子之言似谓宁子之沉晦如愚。免君于患。而读者恐或误看以自免其患为不可及。则大失本意也。家语。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卒。太史公史记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而只称蚤死者。必以家语为可疑故也。盖如家语则颜子卒适当孔子六十二岁。鲤也未死之前也。王肃虽疑年数之错误。而不能明辨核实。朱子注论语。颜子卒。颜路请车而特书。孔子时已致仕。小注问回之死先于鲤。故有以鲤也死为夫子之设言者。朱子但言人情之不应如此。而亦无鲤与颜子生卒之可据矣。今按史记孔子世家。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又按家语。孔子十九娶幵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卒。则孔子六十九岁时也。又按孔子通纪。颜子少孔子三十八岁。而孔子七十岁。颜渊死云。则颜子之卒。正合三十二岁。后于伯鱼之卒一岁矣。以此观之。则以鲤也死为孔子之设言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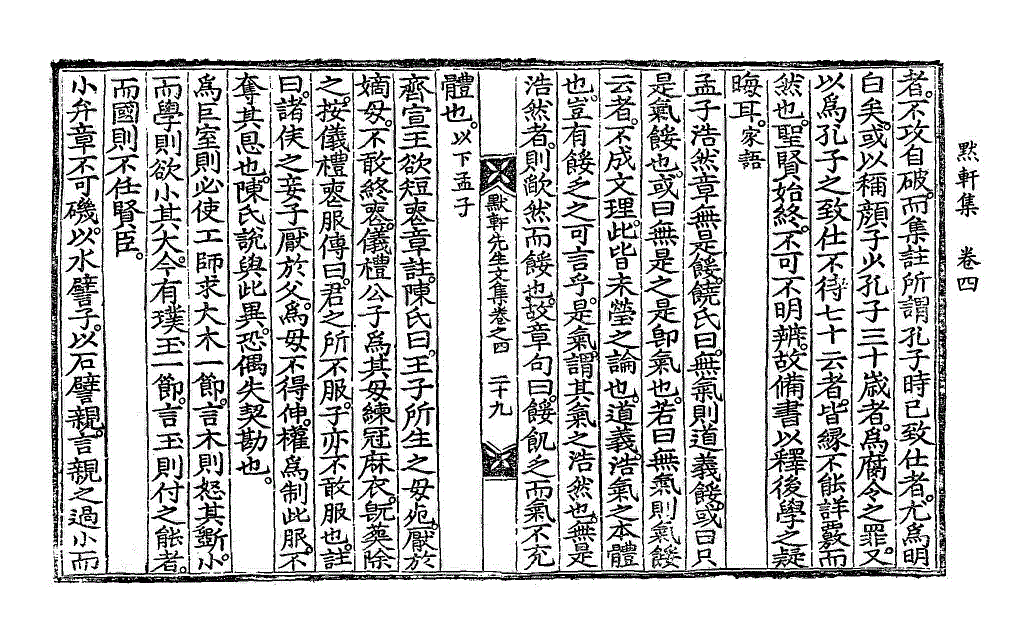 者。不攻自破。而集注所谓孔子时已致仕者。尤为明白矣。或以称颜子少孔子三十岁者。为腐令之罪。又以为孔子之致仕不待七十云者。皆缘不能详覈而然也。圣贤始终。不可不明辨。故备书以释后学之疑晦耳。(家语)
者。不攻自破。而集注所谓孔子时已致仕者。尤为明白矣。或以称颜子少孔子三十岁者。为腐令之罪。又以为孔子之致仕不待七十云者。皆缘不能详覈而然也。圣贤始终。不可不明辨。故备书以释后学之疑晦耳。(家语)孟子浩然章无是馁。饶氏曰。无气则道义馁。或曰只是气馁也。或曰无是之是即气也。若曰无气则气馁云者。不成文理。此皆未莹之论也。道义。浩气之本体也。岂有馁乏之可言乎。是气。谓其气之浩然也。无是浩然者。则欿然而馁也。故章句曰。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以下孟子)
齐宣王欲短丧章注。陈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厌于嫡母。不敢终丧。仪礼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既葬除之。按仪礼丧服传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曰。诸侯之妾子厌于父。为母不得伸。权为制此服。不夺其恩也。陈氏说与此异。恐偶失契勘也。
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一节。言木则怒其斲。小而学则欲小其大。今有璞玉一节。言玉则付之能者。而国则不任贤臣。
小弁章不可矶。以水譬子。以石譬亲。言亲之过小而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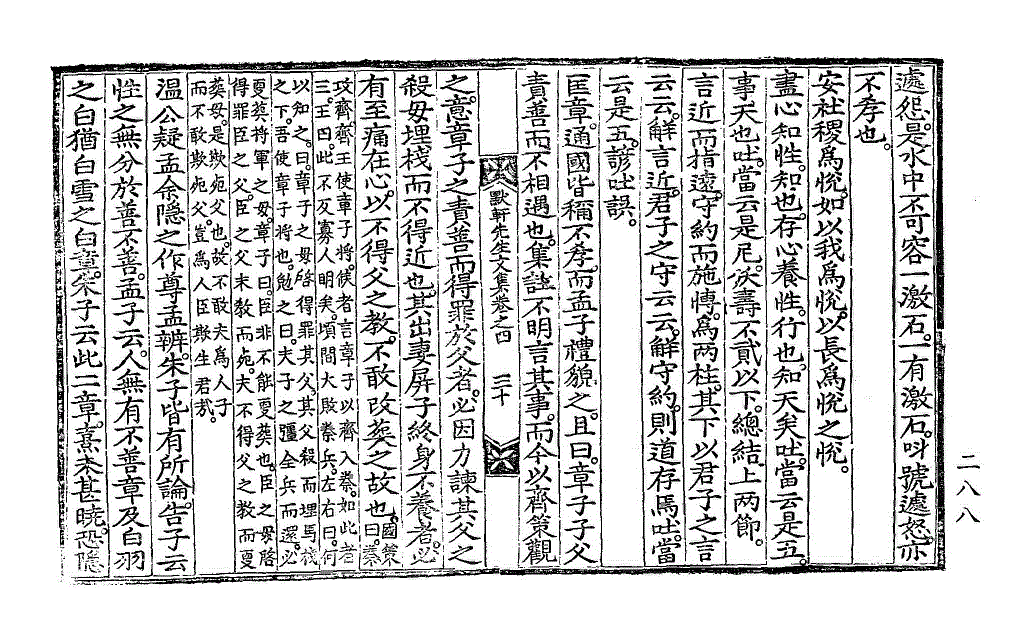 遽怨。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叫号遽怒。亦不孝也。
遽怨。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叫号遽怒。亦不孝也。安社稷为悦。如以我为悦。以长为悦之悦。
尽心知性。知也。存心养性。行也。知天矣吐。当云是五。事天也吐。当云是尼。夭寿不贰以下。总结上两节。
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为两柱。其下以君子之言云云。解言近。君子之守云云。解守约。则道存焉吐。当云是五。谚吐误。
匡章。通国皆称不孝。而孟子礼貌之。且曰。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集注不明言其事。而今以齐策观之。意章子之责善而得罪于父者。必因力谏其父之杀母埋栈而不得近也。其出妻屏子终身不养者。必有至痛在心。以不得父之教。不敢改葬之故也。(国策曰。秦攻齐。齐王使章子将。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如此者三。王曰。此不反寡人明矣。顷间大败秦兵。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而埋马栈之下。吾使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彊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敢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温公疑孟余隐之作尊孟辨。朱子皆有所论。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孟子云。人无有不善章及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章。朱子云此二章。熹未甚晓。恐隐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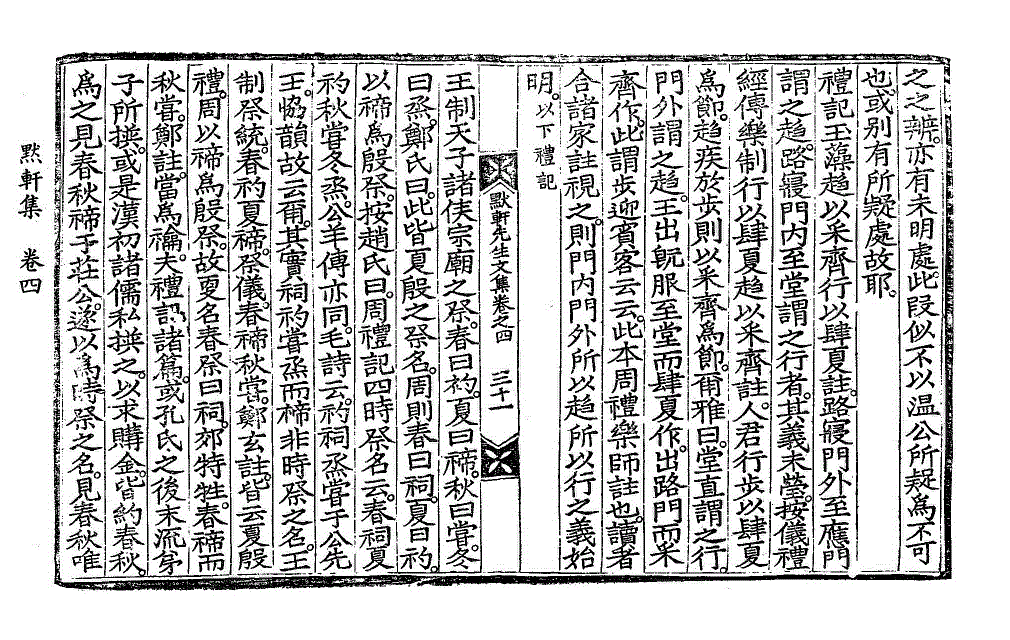 之之辨。亦有未明处。此段似不以温公所疑为不可也。或别有所疑处故耶。
之之辨。亦有未明处。此段似不以温公所疑为不可也。或别有所疑处故耶。礼记玉藻趋以采齐行以肆夏注。路寝门外至应门谓之趋。路寝门内至堂谓之行者。其义未莹。按仪礼经传乐制行以肆夏趋以采齐注。人君行步以肆夏为节。趋疾于步则以采齐为节。尔雅曰。堂直谓之行。门外谓之趋。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门而采齐作。此谓步迎宾客云云。此本周礼乐师注也。读者合诸家注视之。则门内门外所以趋所以行之义始明。(以下礼记)
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郑氏曰。此皆夏殷之祭名。周则春曰祠。夏曰礿。以禘为殷祭。按赵氏曰。周礼记四时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公羊传亦同。毛诗云。礿祠烝尝于公先王。协韵故云尔。其实祠礿尝烝而禘非时祭之名。王制祭统。春礿夏禘。祭仪。春禘秋尝。郑玄注。皆云夏殷礼。周以禘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尝。郑注。当为礿。夫礼记诸篇。或孔氏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撰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见春秋禘于庄公。遂以为时祭之名。见春秋唯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89L 页
 两度书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谓之春。或谓之夏。各自著书。不相符合。郑玄不达其意。故主异说。且祭统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汪氏曰。闵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记礼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时。交互不同。遂误为时祭。此二注。见春秋闵公二年禘于庄公胡传注。
两度书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谓之春。或谓之夏。各自著书。不相符合。郑玄不达其意。故主异说。且祭统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汪氏曰。闵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记礼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时。交互不同。遂误为时祭。此二注。见春秋闵公二年禘于庄公胡传注。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注。武宿夜其义未闻。按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朝。因名为武宿夜。见仪礼经传乐舞。孔子闲居。耆欲将至。有开必先。按语类曰。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讹为耆欲。其兆讹为有开。丧服小记宗子母在为妻禫注。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按仪礼疏曰。贺玚云。父在适子为妻不禫。若父殁母存则得禫。宗子尚然则其馀适子母在为妻禫可知。小记云。父在为妻以杖即位。郑玄云。庶子为妻。贺循云。妇人尊微。不夺正服。又云。非宗子。其馀母在不禫。自相矛盾矣。庶子父在犹杖而禫。则岂有母在不禫之理乎。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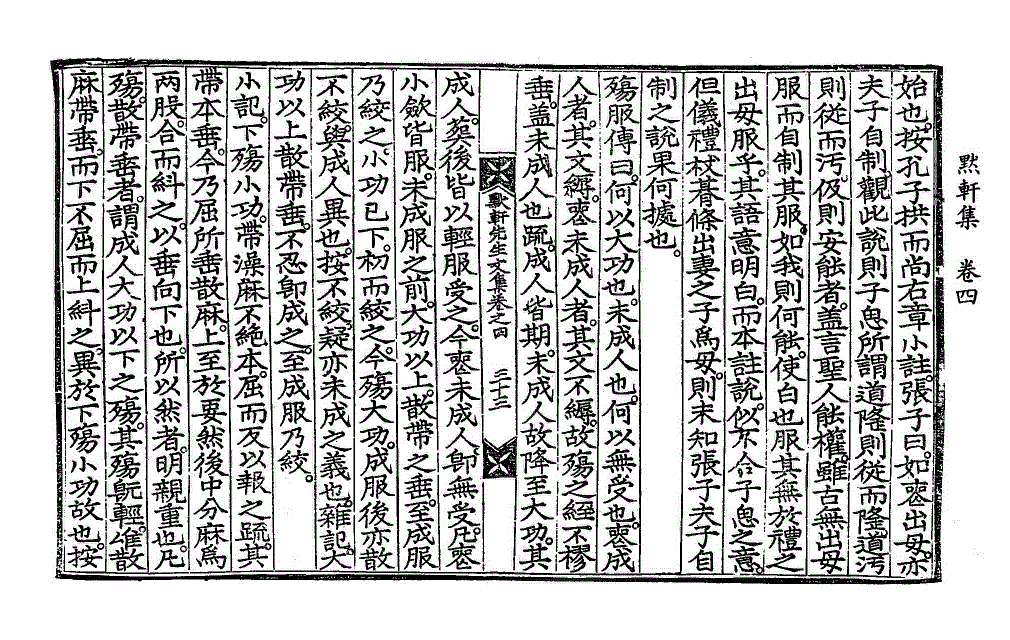 始也。按孔子拱而尚右章小注。张子曰。如丧出母。亦夫子自制。观此说则子思所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者。盖言圣人能权。虽古无出母服而自制其服。如我则何能。使白也服其无于礼之出母服乎。其语意明白。而本注说。似不合子思之意。但仪礼杖期条出妻之子为母。则未知张子夫子自制之说果何据也。
始也。按孔子拱而尚右章小注。张子曰。如丧出母。亦夫子自制。观此说则子思所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者。盖言圣人能权。虽古无出母服而自制其服。如我则何能。使白也服其无于礼之出母服乎。其语意明白。而本注说。似不合子思之意。但仪礼杖期条出妻之子为母。则未知张子夫子自制之说果何据也。殇服传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缛。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缛。故殇之经不樛垂。盖未成人也疏。成人皆期。未成人故降至大功。其成人。葬后皆以轻服受之。今丧未成人。即无受。凡丧小敛皆服。未成服之前。大功以上。散带之垂。至成服乃绞之。小功已下。初而绞之。今殇大功。成服后亦散不绞。与成人异也。按不绞。疑亦未成之义也。杂记。大功以上散带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绞。
小记。下殇小功。带澡麻不绝本。屈而反以报之疏。其带本垂。今乃屈所垂散麻。上至于要然后中分麻为两股。合而纠之。以垂向下也。所以然者。明亲重也。凡殇。散带垂者。谓成人大功以下之殇。其殇既轻。唯散麻带垂。而下不屈而上纠之。异于下殇小功故也。按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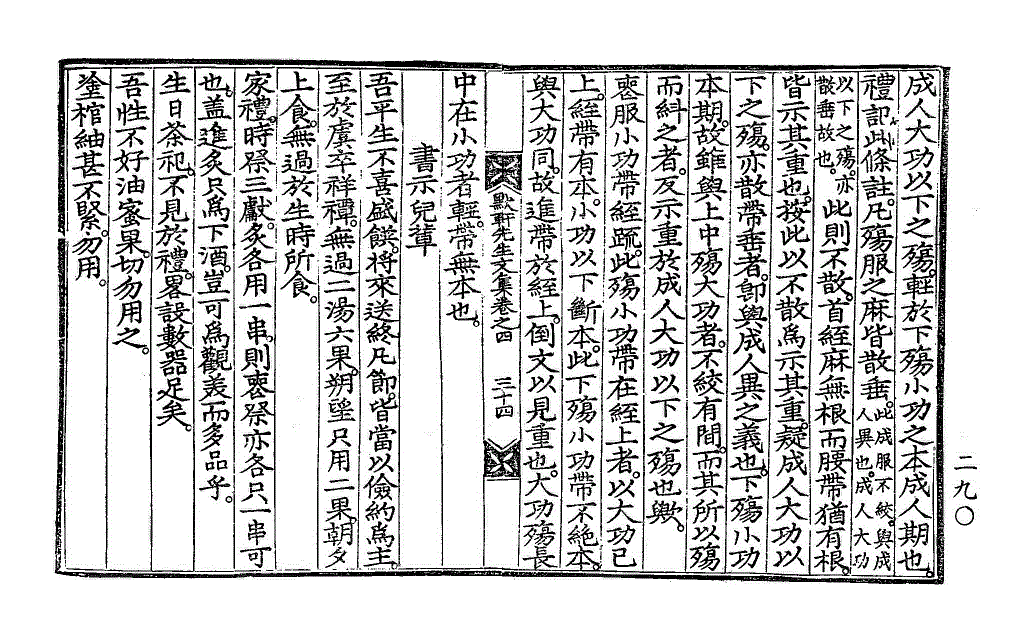 成人大功以下之殇。轻于下殇小功之本成人期也。礼记此条注。凡殇服之麻皆散垂。(此成服不绞。与成人异也。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亦散垂故也。)此则不散。首绖麻无根而腰带犹有根。皆示其重也。按此以不散为示其重。疑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亦散带垂者。即与成人异之义也。下殇小功本期。故虽与上中殇大功者。不绞有间。而其所以殇而纠之者。反示重于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也欤。
成人大功以下之殇。轻于下殇小功之本成人期也。礼记此条注。凡殇服之麻皆散垂。(此成服不绞。与成人异也。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亦散垂故也。)此则不散。首绖麻无根而腰带犹有根。皆示其重也。按此以不散为示其重。疑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亦散带垂者。即与成人异之义也。下殇小功本期。故虽与上中殇大功者。不绞有间。而其所以殇而纠之者。反示重于成人大功以下之殇也欤。丧服小功带绖疏。此殇小功带在绖上者。以大功已上。绖带有本。小功以下断本。此下殇小功带不绝本。与大功同。故进带于绖上。倒文以见重也。大功殇长中在小功者轻。带无本也。
书示儿辈
吾平生不喜盛馔。将来送终凡节。皆当以俭约为主。至于虞卒祥禫。无过二汤六果。朔望只用二果。朝夕上食。无过于生时所食。
家礼。时祭三献。炙各用一串。则丧祭亦各只一串可也。盖进炙只为下酒。岂可为观美而多品乎。
生日茶祀。不见于礼。略设数器足矣。
吾性不好油蜜果。切勿用之。
涂棺䌷甚不紧。勿用。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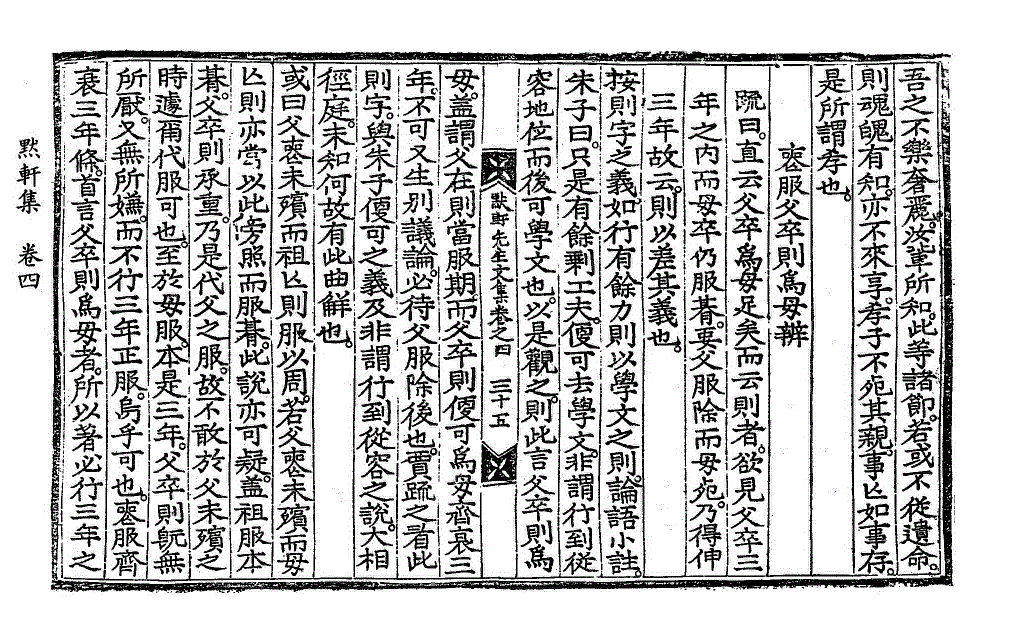 吾之不乐奢丽。汝辈所知。此等诸节。若或不从遗命。则魂魄有知。亦不来享。孝子不死其亲。事亡如事存。是所谓孝也。
吾之不乐奢丽。汝辈所知。此等诸节。若或不从遗命。则魂魄有知。亦不来享。孝子不死其亲。事亡如事存。是所谓孝也。丧服父卒则为母辨
疏曰。直云父卒为母足矣而云则者。欲见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则以差其义也。
按则字之义。如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之则。论语小注。朱子曰。只是有馀剩工夫。便可去学文。非谓行到从容地位而后可学文也。以是观之。则此言父卒则为母。盖谓父在则当服期。而父卒则便可为母齐衰三年。不可又生别议论。必待父服除后也。贾疏之看此则字。与朱子便可之义及非谓行到从容之说。大相径庭。未知何故有此曲解也。
或曰父丧未殡而祖亡则服以周。若父丧未殡而母亡则亦当以此傍照而服期。此说亦可疑。盖祖服本期。父卒则承重。乃是代父之服。故不敢于父未殡之时遽尔代服可也。至于母服。本是三年。父卒则既无所厌。又无所嫌。而不行三年正服。乌乎可也。丧服齐衰三年条。首言父卒则为母者。所以著必行三年之
默轩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91L 页
 义也。今乃不遵礼经正文。而只以后儒之说。傍照短丧。千万不可。愚伏礼疑从厚之训。恐合礼意也。
义也。今乃不遵礼经正文。而只以后儒之说。傍照短丧。千万不可。愚伏礼疑从厚之训。恐合礼意也。丧礼备要小敛时孝巾辨
世俗袭后或小敛之时。丧人着孝巾。似从沙溪说。而按仪礼小敛冯尸后主人髺发袒众主人免于房注。髺发者去笄纚而紒。免者将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丧大记主人袒脱髦括发以麻。司马温公虽有齐衰以下着巾加免于其上亦可之说。而本非古礼。(见家礼。)况又有主人不冠之明文乎。且仪礼注疏众主人齐衰以下非众子云。众主人犹以免代冠则丧人岂可戴巾乎。沙溪从杂记疏及丘氏之说而有白布巾之云。恐非古礼及家礼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