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青城集卷之八 第 x 页
青城集卷之八(昌山成大中士执 著)
论
论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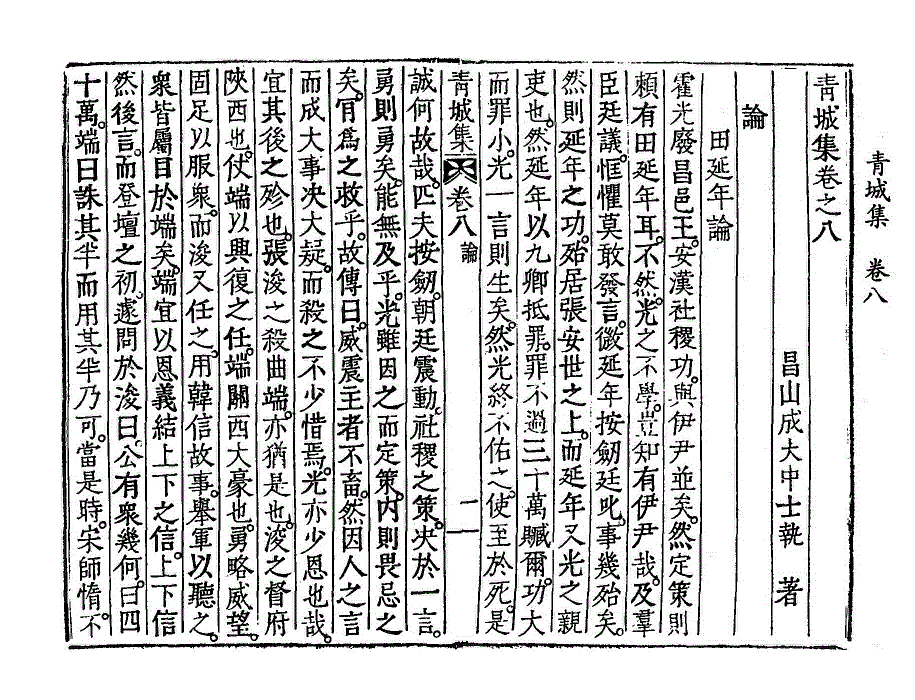 田延年论
田延年论霍光废昌邑王。安汉社稷功。与伊尹并矣。然定策则赖有田延年耳。不然。光之不学。岂知有伊尹哉。及群臣廷议。恇惧莫敢发言。微延年按剑廷叱。事几殆矣。然则延年之功。殆居张安世之上。而延年又光之亲吏也。然延年以九卿抵罪。罪不过三十万赃尔。功大而罪小。光一言则生矣。然光终不佑之。使至于死。是诚何故哉。匹夫按剑。朝廷震动。社稷之策。决于一言。勇则勇矣。能无及乎。光虽因之而定策。内则畏忌之矣。肯为之救乎。故传曰。威震主者不畜。然因人之言而成大事决大疑。而杀之不少惜焉。光亦少恩也哉。宜其后之殄也。张浚之杀曲端。亦犹是也。浚之督府陕西也。仗端以兴复之任。端关西大豪也。勇略威望。固足以服众。而浚又任之。用韩信故事。举军以听之。众皆属目于端矣。端宜以恩义结上下之信。上下信然后言。而登坛之初。遽问于浚曰。公有众几何。曰四十万。端曰诛其半而用其半乃可。当是时。宋师惰。不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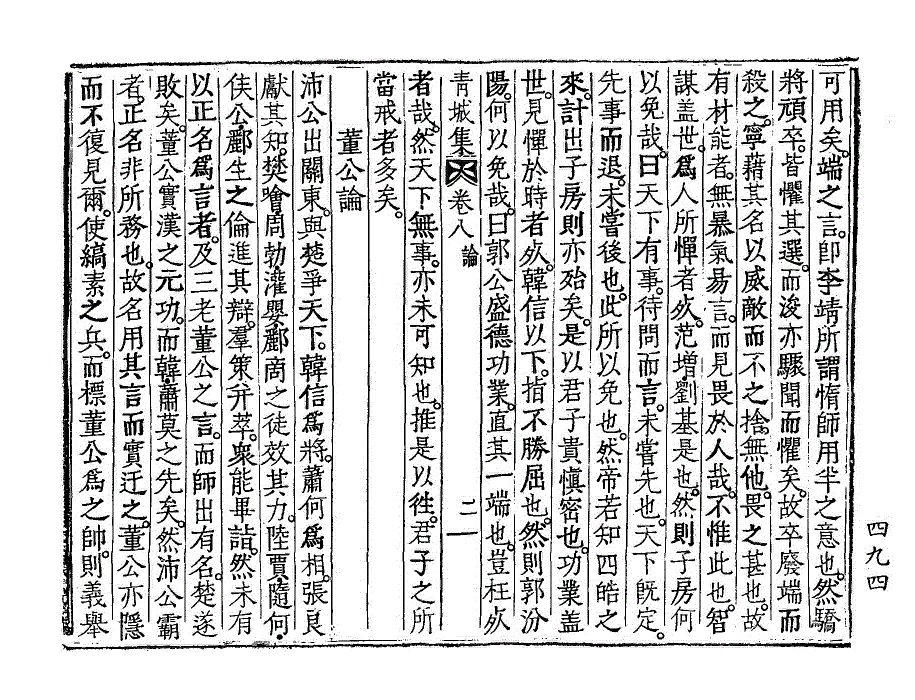 可用矣。端之言。即李靖所谓惰师用半之意也。然骄将顽卒。皆惧其选。而浚亦骤闻而惧矣。故卒废端而杀之。宁藉其名以威敌而不之舍。无他。畏之甚也。故有材能者。无暴气易言。而见畏于人哉。不惟此也。智谋盖世。为人所惮者死。范增,刘基是也。然则子房何以免哉。曰天下有事。待问而言。未尝先也。天下既定。先事而退。未尝后也。此所以免也。然帝若知四皓之来。计出子房则亦殆矣。是以君子贵慎密也。功业盖世。见惮于时者死。韩信以下。指不胜屈也。然则郭汾阳。何以免哉。曰郭公盛德功业。直其一端也。岂枉死者哉。然天下无事。亦未可知也。推是以往。君子之所当戒者多矣。
可用矣。端之言。即李靖所谓惰师用半之意也。然骄将顽卒。皆惧其选。而浚亦骤闻而惧矣。故卒废端而杀之。宁藉其名以威敌而不之舍。无他。畏之甚也。故有材能者。无暴气易言。而见畏于人哉。不惟此也。智谋盖世。为人所惮者死。范增,刘基是也。然则子房何以免哉。曰天下有事。待问而言。未尝先也。天下既定。先事而退。未尝后也。此所以免也。然帝若知四皓之来。计出子房则亦殆矣。是以君子贵慎密也。功业盖世。见惮于时者死。韩信以下。指不胜屈也。然则郭汾阳。何以免哉。曰郭公盛德功业。直其一端也。岂枉死者哉。然天下无事。亦未可知也。推是以往。君子之所当戒者多矣。董公论
沛公出关东。与楚争天下。韩信为将。萧何为相。张良献其知。樊哙,周勃,灌婴,郦啇之徒效其力。陆贾,随何,侯公,郦生之伦进其辩。群策并萃。众能毕诣。然未有以正名为言者。及三老董公之言。而师出有名。楚遂败矣。蕫公实汉之元功。而韩,萧莫之先矣。然沛公霸者。正名非所务也。故名用其言而实迂之。董公亦隐而不复见尔。使缟素之兵。而标董公为之帅。则义举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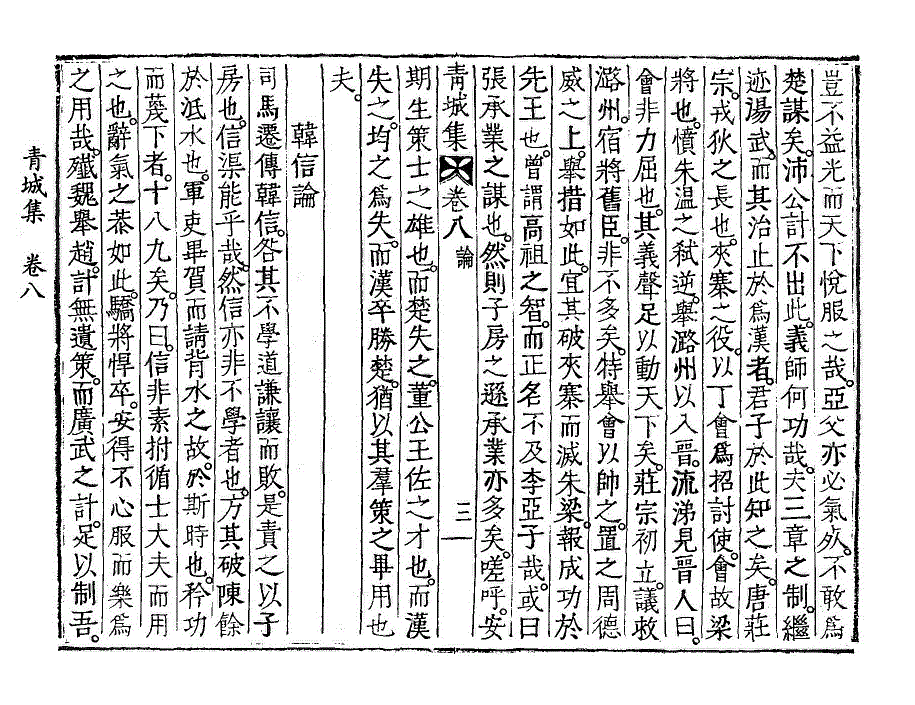 岂不益光而天下悦服之哉。亚父亦必气死。不敢为楚谋矣。沛公计不出此。义师何功哉。夫三章之制。继迹汤武。而其治止于为汉者。君子于此知之矣。唐庄宗。戎狄之长也。夹寨之役。以丁会为招讨使。会故梁将也。愤朱温之弑逆。举潞州以入晋。流涕见晋人曰。会非力屈也。其义声足以动天下矣。庄宗初立。议救潞州。宿将旧臣。非不多矣。特举会以帅之。置之周德威之上。举措如此。宜其破夹寨而灭朱梁。报成功于先王也。曾谓高祖之智。而正名不及李亚子哉。或曰张承业之谋也。然则子房之逊承业亦多矣。嗟呼。安期生策士之雄也。而楚失之。董公王佐之才也。而汉失之。均之为失。而汉卒胜楚。犹以其群策之毕用也夫。
岂不益光而天下悦服之哉。亚父亦必气死。不敢为楚谋矣。沛公计不出此。义师何功哉。夫三章之制。继迹汤武。而其治止于为汉者。君子于此知之矣。唐庄宗。戎狄之长也。夹寨之役。以丁会为招讨使。会故梁将也。愤朱温之弑逆。举潞州以入晋。流涕见晋人曰。会非力屈也。其义声足以动天下矣。庄宗初立。议救潞州。宿将旧臣。非不多矣。特举会以帅之。置之周德威之上。举措如此。宜其破夹寨而灭朱梁。报成功于先王也。曾谓高祖之智。而正名不及李亚子哉。或曰张承业之谋也。然则子房之逊承业亦多矣。嗟呼。安期生策士之雄也。而楚失之。董公王佐之才也。而汉失之。均之为失。而汉卒胜楚。犹以其群策之毕用也夫。韩信论
司马迁传韩信。咎其不学道谦让而败。是责之以子房也。信渠能乎哉。然信亦非不学者也。方其破陈馀于泜水也。军吏毕贺而请背水之故。于斯时也。矜功而蔑下者。十八九矣。乃曰。信非素拊循士大夫而用之也。辞气之恭如此。骄将悍卒。安得不心服而乐为之用哉。歼魏举赵。计无遗策。而广武之计。足以制吾。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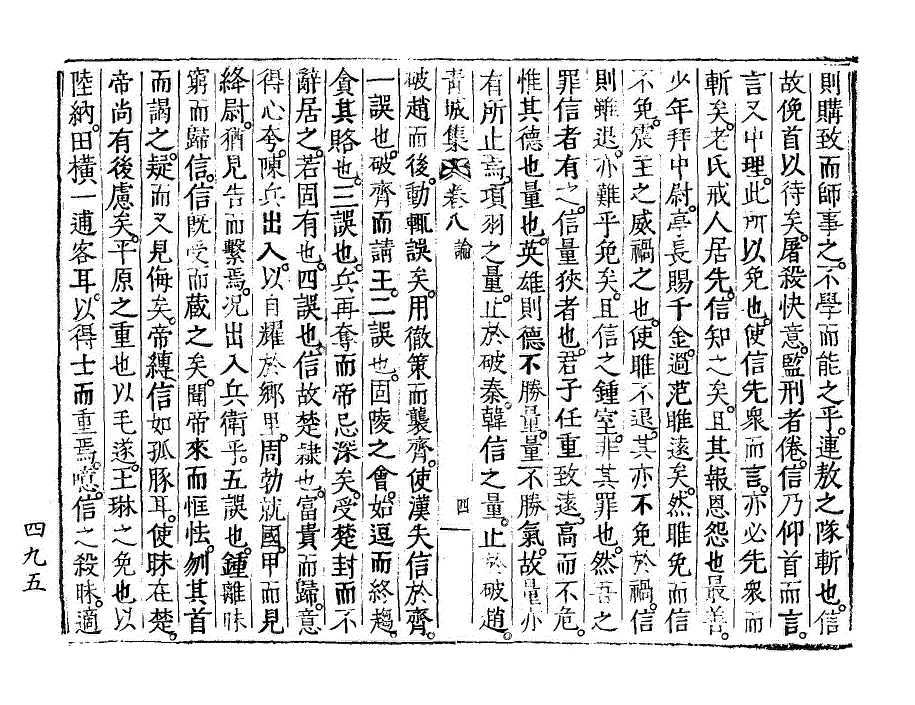 则购致而师事之。不学而能之乎。连敖之队斩也。信故俛首以待矣。屠杀快意。监刑者倦。信乃仰首而言。言又中理。此所以免也。使信先众而言。亦必先众而斩矣。老氏戒人居先。信知之矣。且其报恩怨也最善。少年拜中尉。亭长赐千金。过范雎远矣。然雎免而信不免。震主之威祸之也。使雎不退。其亦不免于祸。信则虽退。亦难乎免矣。且信之钟室。非其罪也。然吾之罪信者有之。信量狭者也。君子任重致远。高而不危。惟其德也量也。英雄则德不胜量。量不胜气。故量亦有所止焉。项羽之量。止于破秦。韩信之量。止于破赵。破赵而后。动辄误矣。用彻策而袭齐。使汉失信于齐。一误也。破齐而请王。二误也。固陵之会。始逗而终趋。贪其赂也。三误也。兵再夺而帝忌深矣。受楚封而不辞居之。若固有也。四误也。信故楚隶也。富贵而归。意得心夸。陈兵出入。以自耀于乡里。周勃就国。甲而见绛尉。犹见告而系焉。况出入兵卫乎。五误也。钟离昧穷而归信。信既受而藏之矣。闻帝来而恇怯。刎其首而谒之。疑而又见侮矣。帝缚信如孤豚耳。使昧在楚。帝尚有后虑矣。平原之重也以毛遂。王琳之免也以陆纳。田横一逋客耳。以得士而重焉。噫。信之杀昧。适
则购致而师事之。不学而能之乎。连敖之队斩也。信故俛首以待矣。屠杀快意。监刑者倦。信乃仰首而言。言又中理。此所以免也。使信先众而言。亦必先众而斩矣。老氏戒人居先。信知之矣。且其报恩怨也最善。少年拜中尉。亭长赐千金。过范雎远矣。然雎免而信不免。震主之威祸之也。使雎不退。其亦不免于祸。信则虽退。亦难乎免矣。且信之钟室。非其罪也。然吾之罪信者有之。信量狭者也。君子任重致远。高而不危。惟其德也量也。英雄则德不胜量。量不胜气。故量亦有所止焉。项羽之量。止于破秦。韩信之量。止于破赵。破赵而后。动辄误矣。用彻策而袭齐。使汉失信于齐。一误也。破齐而请王。二误也。固陵之会。始逗而终趋。贪其赂也。三误也。兵再夺而帝忌深矣。受楚封而不辞居之。若固有也。四误也。信故楚隶也。富贵而归。意得心夸。陈兵出入。以自耀于乡里。周勃就国。甲而见绛尉。犹见告而系焉。况出入兵卫乎。五误也。钟离昧穷而归信。信既受而藏之矣。闻帝来而恇怯。刎其首而谒之。疑而又见侮矣。帝缚信如孤豚耳。使昧在楚。帝尚有后虑矣。平原之重也以毛遂。王琳之免也以陆纳。田横一逋客耳。以得士而重焉。噫。信之杀昧。适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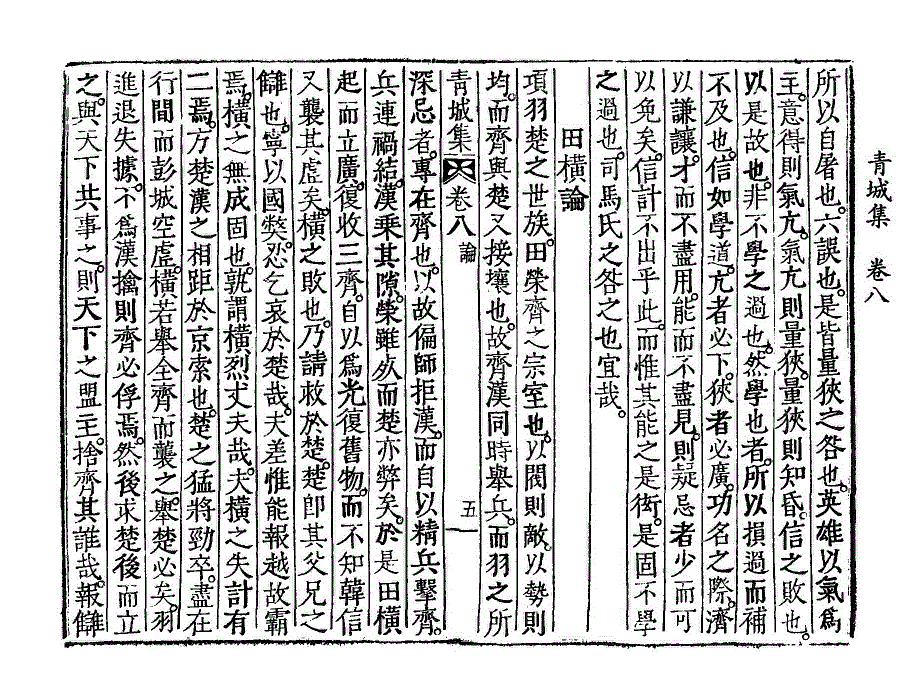 所以自屠也。六误也。是皆量狭之咎也。英雄以气为主。意得则气亢。气亢则量狭。量狭则知昏。信之败也。以是故也。非不学之过也。然学也者。所以损过而补不及也。信如学道。亢者必下。狭者必广。功名之际。济以谦让。才而不尽用。能而不尽见。则疑忌者少而可以免矣。信计不出乎此。而惟其能之是衒。是固不学之过也。司马氏之咎之也宜哉。
所以自屠也。六误也。是皆量狭之咎也。英雄以气为主。意得则气亢。气亢则量狭。量狭则知昏。信之败也。以是故也。非不学之过也。然学也者。所以损过而补不及也。信如学道。亢者必下。狭者必广。功名之际。济以谦让。才而不尽用。能而不尽见。则疑忌者少而可以免矣。信计不出乎此。而惟其能之是衒。是固不学之过也。司马氏之咎之也宜哉。田横论
项羽楚之世族。田荣齐之宗室也。以阀则敌。以势则均。而齐与楚又接壤也。故齐汉同时举兵。而羽之所深忌者。专在齐也。以故偏师拒汉。而自以精兵击齐。兵连祸结。汉乘其隙。荣虽死而楚亦弊矣。于是田横起而立广。复收三齐。自以为光复旧物。而不知韩信又袭其虚矣。横之败也。乃请救于楚。楚即其父兄之雠也。宁以国弊。忍乞哀于楚哉。夫差惟能报越故霸焉。横之无成固也。孰谓横烈丈夫哉。夫横之失计有二焉。方楚汉之相距于京索也。楚之猛将劲卒。尽在行间而彭城空虚。横若举全齐而袭之。举楚必矣。羽进退失据。不为汉擒则齐必俘焉。然后求楚后而立之。与天下共事之。则天下之盟主。舍齐其谁哉。报雠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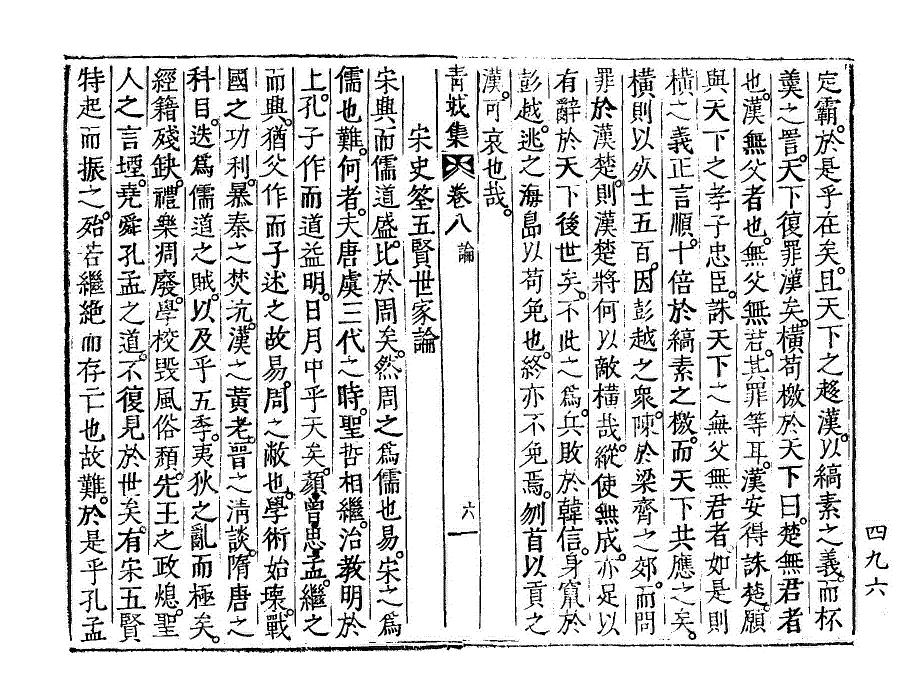 定霸。于是乎在矣。且天下之趍汉。以缟素之义。而杯羹之詈。天下复罪汉矣。横苟檄于天下曰。楚无君者也。汉无父者也。无父无君。其罪等耳。汉安得诛楚。愿与天下之孝子忠臣。诛天下之无父无君者。如是则横之义正言顺。十倍于缟素之檄。而天下共应之矣。横则以死士五百。因彭越之众。陈于梁齐之郊。而问罪于汉楚。则汉楚将何以敌横哉。纵使无成。亦足以有辞于天下后世矣。不此之为。兵败于韩信。身窜于彭越。逃之海岛以苟免也。终亦不免焉。刎首以贡之汉。可哀也哉。
定霸。于是乎在矣。且天下之趍汉。以缟素之义。而杯羹之詈。天下复罪汉矣。横苟檄于天下曰。楚无君者也。汉无父者也。无父无君。其罪等耳。汉安得诛楚。愿与天下之孝子忠臣。诛天下之无父无君者。如是则横之义正言顺。十倍于缟素之檄。而天下共应之矣。横则以死士五百。因彭越之众。陈于梁齐之郊。而问罪于汉楚。则汉楚将何以敌横哉。纵使无成。亦足以有辞于天下后世矣。不此之为。兵败于韩信。身窜于彭越。逃之海岛以苟免也。终亦不免焉。刎首以贡之汉。可哀也哉。宋史筌五贤世家论
宋兴而儒道盛。比于周矣。然周之为儒也易。宋之为儒也难。何者。夫唐虞三代之时。圣哲相继。治教明于上。孔子作而道益明。日月中乎天矣。颜,曾,思,孟。继之而兴。犹父作而子述之故易。周之敝也。学术始坏。战国之功利。暴秦之焚坑。汉之黄老。晋之清谈。隋唐之科目。迭为儒道之贼。以及乎五季。夷狄之乱而极矣。经籍残缺。礼乐凋废。学校毁风俗颓。先王之政熄。圣人之言堙。尧舜孔孟之道。不复见于世矣。有宋五贤特起而振之。殆若继绝而存亡也故难。于是乎孔孟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7H 页
 之道复明。宋之治教。比隆三代。寔五贤之力也。旧史列之道学。知尊乎儒林矣。然犹之与谢游张黄比也。故别之为五贤世家。升之宰辅之上。以表儒宗。
之道复明。宋之治教。比隆三代。寔五贤之力也。旧史列之道学。知尊乎儒林矣。然犹之与谢游张黄比也。故别之为五贤世家。升之宰辅之上。以表儒宗。青城集卷之八(昌山成大中士执 著)
说
思说
管子曰。思之又思。鬼神其通之。夫道之妙者。得之也难。思之而辄通者。必非其至者也。思之而不得。逾益思之。愤悱发于面䫉。穷格达于幽眇。夫然后通。若有物相之。是所谓鬼神也。鬼神本在吾心。岂可外求哉。然是说也人多疑之。不思故也。纵或思之。不深故也。吾尝用之于文矣。始则戛戛乎无所得。芒芒乎无所见矣。然吾益整吾䫉一吾虑。思之益深。则忽若有缕烟生焉。氤氲纠结。自下而上。少焉变而为萤。闪荧琐细。烂若碎星。或聚或散。忽近忽远。吾既见其兆矣。操之逾固。引之逾急。则众幺俱息。而倏若有梁柱者峙于前矣。于是遽起而从之。惟吾笔之所适而文成焉。思至于此。鬼神亦避其锐矣。吾又进之于易。竭吾思而求之三年。卦画灿然并列于前。经义之未通者。必得之梦寐。不知者必以吾为诞矣。然思之实难。方其思之而未得也。神栖于木。眼坠于渊。听无闻食无味。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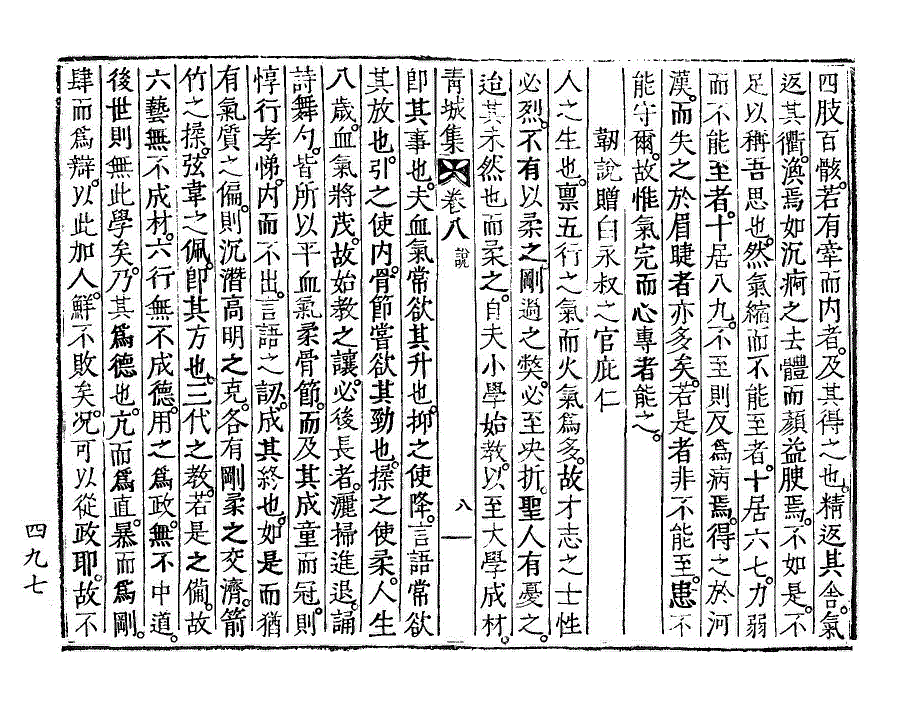 四肢百骸。若有牵而内者。及其得之也。精返其舍。气返其衢。涣焉如沉痾之去体而颜益腴焉。不如是。不足以称吾思也。然气缩而不能至者。十居六七。力弱而不能至者。十居八九。不至则反为病焉。得之于河汉。而失之于眉睫者亦多矣。若是者非不能至。患不能守尔。故惟气完而心专者能之。
四肢百骸。若有牵而内者。及其得之也。精返其舍。气返其衢。涣焉如沉痾之去体而颜益腴焉。不如是。不足以称吾思也。然气缩而不能至者。十居六七。力弱而不能至者。十居八九。不至则反为病焉。得之于河汉。而失之于眉睫者亦多矣。若是者非不能至。患不能守尔。故惟气完而心专者能之。韧说赠白永叔之官庇仁
人之生也。禀五行之气而火气为多。故才志之士性必烈。不有以柔之。刚过之弊。必至决折。圣人有忧之。迨其未然也而柔之。自夫小学始教。以至大学成材。即其事也。夫血气常欲其升也。抑之使降。言语常欲其放也。引之使内。骨节尝欲其劲也。揉之使柔。人生八岁。血气将茂。故始教之让。必后长者。洒扫进退。诵诗舞勺。皆所以平血气柔骨节。而及其成童而冠。则惇行孝悌。内而不出。言语之讱。成其终也。如是而犹有气质之偏。则沉潜高明之克。各有刚柔之交济。箭竹之揉。弦韦之佩。即其方也。三代之教。若是之备。故六艺无不成材。六行无不成德。用之为政。无不中道。后世则无此学矣。乃其为德也。亢而为直。暴而为刚。肆而为辩。以此加人。鲜不败矣。况可以从政耶。故不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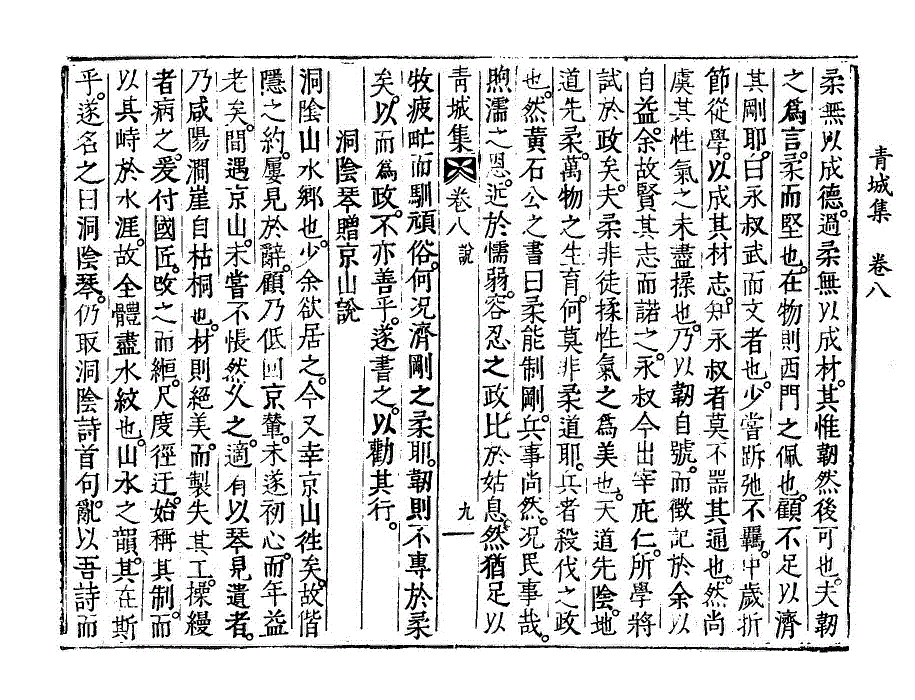 柔无以成德。过柔无以成材。其惟韧然后可也。夫韧之为言。柔而坚也。在物则西门之佩也。顾不足以济其刚耶。白永叔武而文者也。少尝跅弛不羁。中岁折节从学。以成其材志。知永叔者莫不器其通也。然尚虞其性气之未尽揉也。乃以韧自号。而徵记于余以自益。余故贤其志而诺之。永叔今出宰庇仁。所学将试于政矣。夫柔非徒揉性气之为美也。天道先阴。地道先柔。万物之生育。何莫非柔道耶。兵者杀伐之政也。然黄石公之书曰柔能制刚。兵事尚然。况民事哉。煦濡之恩。近于懦弱。容忍之政。比于姑息。然犹足以牧疲氓而驯顽俗。何况济刚之柔耶。韧则不专于柔矣。以而为政。不亦善乎。遂书之。以劝其行。
柔无以成德。过柔无以成材。其惟韧然后可也。夫韧之为言。柔而坚也。在物则西门之佩也。顾不足以济其刚耶。白永叔武而文者也。少尝跅弛不羁。中岁折节从学。以成其材志。知永叔者莫不器其通也。然尚虞其性气之未尽揉也。乃以韧自号。而徵记于余以自益。余故贤其志而诺之。永叔今出宰庇仁。所学将试于政矣。夫柔非徒揉性气之为美也。天道先阴。地道先柔。万物之生育。何莫非柔道耶。兵者杀伐之政也。然黄石公之书曰柔能制刚。兵事尚然。况民事哉。煦濡之恩。近于懦弱。容忍之政。比于姑息。然犹足以牧疲氓而驯顽俗。何况济刚之柔耶。韧则不专于柔矣。以而为政。不亦善乎。遂书之。以劝其行。洞阴琴赠京山说
洞阴山水乡也。少余欲居之。今又幸京山往矣。故偕隐之约。屡见于辞。顾乃低回京辇。未遂初心。而年益老矣。间遇京山。未尝不怅然久之。适有以琴见遗者。乃咸阳涧崖自枯桐也。材则绝美。而制失其工。操缦者病之。爰付国匠。改之而縆。尺度径迂。始称其制。而以其峙于水涯。故全体尽水纹也。山水之韵。其在斯乎。遂名之曰洞阴琴。仍取洞阴诗首句。乱以吾诗而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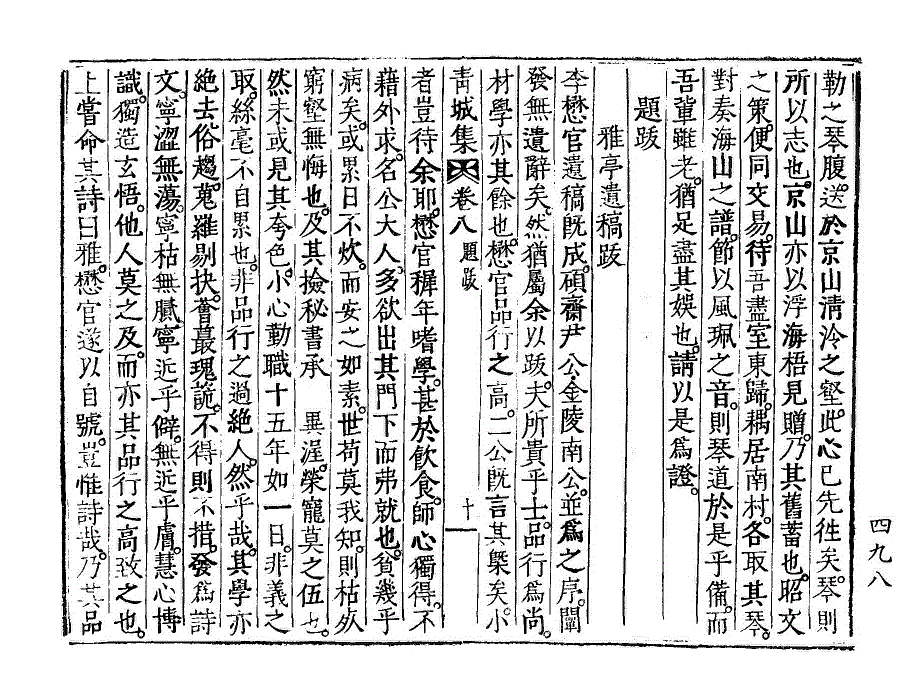 勒之琴腹。送于京山清泠之壑。此心已先往矣。琴则所以志也。京山亦以浮海梧见赠。乃其旧蓄也。昭文之策。便同交易。待吾尽室东归。耦居南村。各取其琴。对奏海山之谱。节以风佩之音。则琴道于是乎备。而吾辈虽老。犹足尽其娱也。请以是为證。
勒之琴腹。送于京山清泠之壑。此心已先往矣。琴则所以志也。京山亦以浮海梧见赠。乃其旧蓄也。昭文之策。便同交易。待吾尽室东归。耦居南村。各取其琴。对奏海山之谱。节以风佩之音。则琴道于是乎备。而吾辈虽老。犹足尽其娱也。请以是为證。青城集卷之八(昌山成大中士执 著)
题跋
雅亭遗稿跋
李懋官遗稿既成。硕斋尹公,金陵南公。并为之序。阐发无遗辞矣。然犹属余以跋。夫所贵乎士。品行为尚。材学亦其馀也。懋官品行之高。二公既言其槩矣。小者岂待余耶。懋官稚年嗜学。甚于饮食。师心独得。不藉外求。名公大人。多欲出其门下而弗就也。贫几乎病矣。或累日不炊。而安之如素。世苟莫我知。则枯死穷壑无悔也。及其捡秘书承 异渥。荣宠莫之伍也。然未或见其夸色。小心勤职十五年如一日。非义之取。丝毫不自累也。非品行之过绝人。然乎哉。其学亦绝去俗趋。蒐罗剔抉。荟蕞瑰诡。不得则不措。发为诗文。宁涩无荡。宁枯无腻。宁近乎僻。无近乎肤。慧心博识。独造玄悟。他人莫之及。而亦其品行之高致之也。上尝命其诗曰雅。懋官遂以自号。岂惟诗哉。乃其品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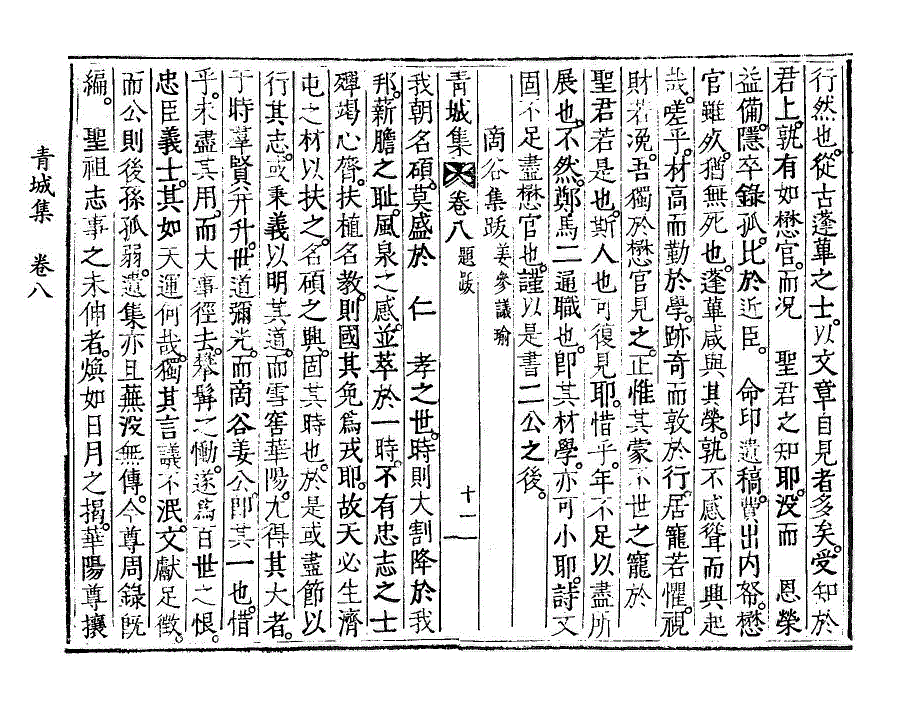 行然也。从古蓬荜之士。以文章自见者多矣。受知于君上。孰有如懋官。而况 圣君之知耶。没而 恩荣益备。隐卒录孤。比于近臣。 命印遗稿。费出内帑。懋官虽死。犹无死也。蓬荜咸与其荣。孰不感耸而兴起哉。嗟乎。材高而勤于学。迹奇而敦于行。居宠若惧。视财若浼。吾独于懋官见之。正惟其蒙不世之宠于 圣君若是也。斯人也可复见耶。惜乎。年不足以尽所展也。不然。郑,马二通职也。即其材学。亦可小耶。诗文固不足尽懋官也。谨以是书二公之后。
行然也。从古蓬荜之士。以文章自见者多矣。受知于君上。孰有如懋官。而况 圣君之知耶。没而 恩荣益备。隐卒录孤。比于近臣。 命印遗稿。费出内帑。懋官虽死。犹无死也。蓬荜咸与其荣。孰不感耸而兴起哉。嗟乎。材高而勤于学。迹奇而敦于行。居宠若惧。视财若浼。吾独于懋官见之。正惟其蒙不世之宠于 圣君若是也。斯人也可复见耶。惜乎。年不足以尽所展也。不然。郑,马二通职也。即其材学。亦可小耶。诗文固不足尽懋官也。谨以是书二公之后。商谷集跋(姜参议瑜)
我朝名硕。莫盛于 仁 孝之世。时则大割降于我邦。薪胆之耻。风泉之感。并萃于一时。不有忠志之士殚竭心膂。扶植名教。则国其免为戎耶。故天必生济屯之材以扶之。名硕之兴。固其时也。于是或尽节以行其志。或秉义以明其道。而雪窖华阳。尤得其大者。于时群贤并升。世道弥光。而商谷姜公。即其一也。惜乎。未尽其用。而大事径去。攀髯之恸。遂为百世之恨。忠臣义士。其如天运何哉。独其言议不泯。文献足徵。而公则后孙孤弱。遗集亦且芜没无传。今尊周录既编。 圣祖志事之未伸者。焕如日月之揭。华阳尊攘
青城集卷之八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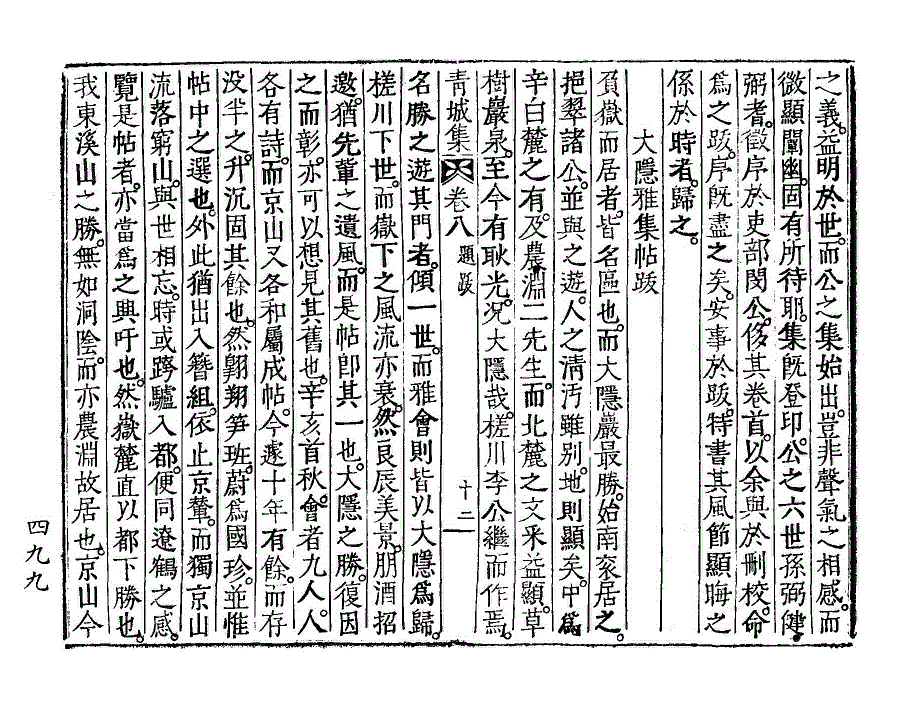 之义。益明于世。而公之集始出。岂非声气之相感。而微显阐幽。固有所待耶。集既登印。公之六世孙弼健,弼耆。徵序于吏部闵公。侈其卷首。以余与于删校。命为之跋。序既尽之矣。安事于跋。特书其风节显晦之系于时者。归之。
之义。益明于世。而公之集始出。岂非声气之相感。而微显阐幽。固有所待耶。集既登印。公之六世孙弼健,弼耆。徵序于吏部闵公。侈其卷首。以余与于删校。命为之跋。序既尽之矣。安事于跋。特书其风节显晦之系于时者。归之。大隐雅集帖跋
负岳而居者。皆名区也。而大隐岩最胜。始南衮居之。挹翠诸公。并与之游。人之清污虽别。地则显矣。中为辛白麓之有。及农,渊二先生。而北麓之文采益显。草树岩泉。至今有耿光。况大隐哉。槎川李公继而作焉。名胜之游其门者。倾一世。而雅会则皆以大隐为归。槎川下世。而岳下之风流亦衰。然良辰美景。朋酒招邀。犹先辈之遗风。而是帖即其一也。大隐之胜。复因之而彰。亦可以想见其旧也。辛亥首秋。会者九人。人各有诗。而京山又各和属成帖。今遽十年有馀。而存没半之。升沉固其馀也。然翱翔笋班。蔚为国珍。并惟帖中之选也。外此犹出入簪组。依止京辇。而独京山流落穷山。与世相忘。时或跨驴入都。便同辽鹤之感。览是帖者。亦当为之兴吁也。然岳麓直以都下胜也。我东溪山之胜。无如洞阴。而亦农渊故居也。京山今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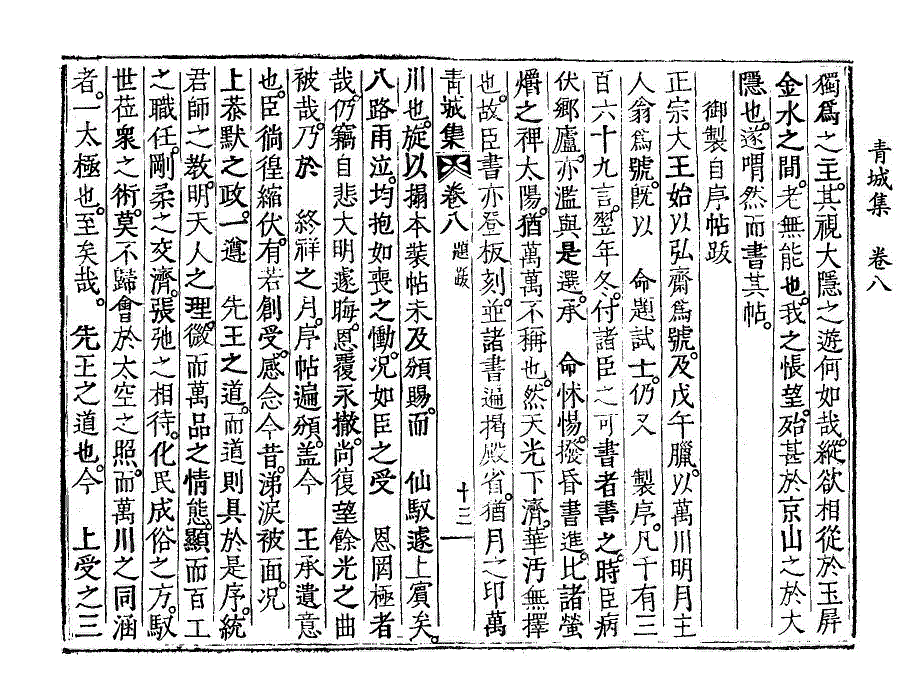 独为之主。其视大隐之游何如哉。纵欲相从于玉屏金水之间。老无能也。我之怅望。殆甚于京山之于大隐也。遂喟然而书其帖。
独为之主。其视大隐之游何如哉。纵欲相从于玉屏金水之间。老无能也。我之怅望。殆甚于京山之于大隐也。遂喟然而书其帖。御制自序帖跋
正宗大王始以弘斋为号。及戊午腊。以万川明月主人翁为号。既以 命题试士。仍又 制序。凡千有三百六十九言。翌年冬。付诸臣之可书者书之。时臣病伏乡庐。亦滥与是选。承 命怵惕。拨昏书进。比诸萤爝之裨太阳。犹万万不称也。然天光下济。华污无择也。故臣书亦登板刻。并诸书遍揭殿省。犹月之印万川也。旋以拓本装帖未及颁赐。而 仙驭遽上宾矣。八路雨泣。均抱如丧之恸。况如臣之受 恩罔极者哉。仍窃自悲大明遽晦。恩覆永撤。尚复望馀光之曲被哉。乃于 终祥之月。序帖遍颁。盖今 王承遗意也。臣徜徨缩伏。有若创受。感念今昔。涕泪被面。况 上恭默之政。一遵 先王之道。而道则具于是序。统君师之教。明天人之理。微而万品之情态。显而百工之职任。刚柔之交济。张弛之相待。化民成俗之方。驭世莅众之术。莫不归会于太空之照。而万川之同涵者。一太极也。至矣哉。 先王之道也。今 上受之三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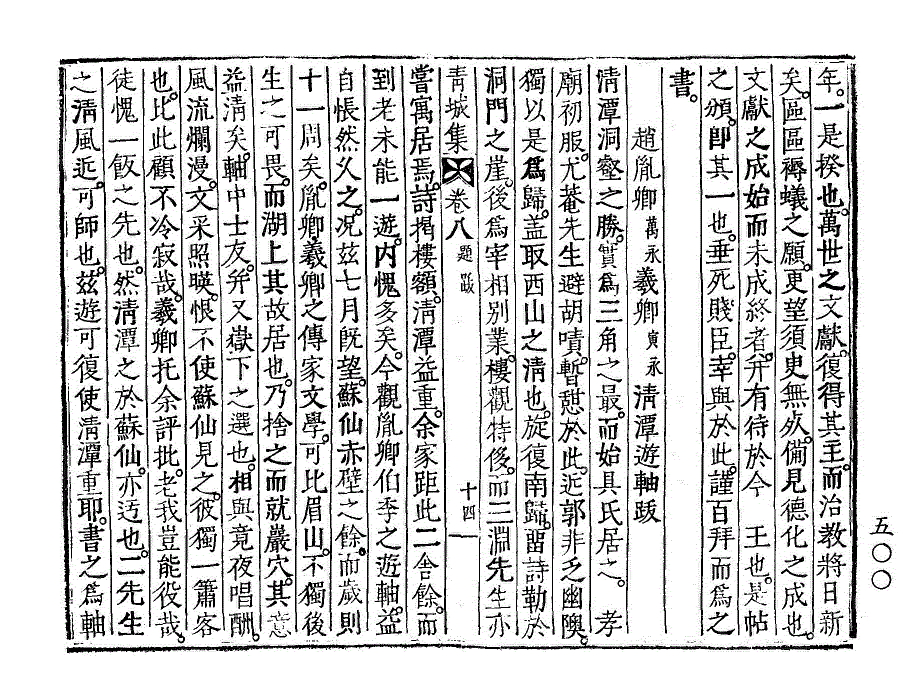 年。一是揆也。万世之文献。复得其主。而治教将日新矣。区区褥蚁之愿。更望须臾无死。备见德化之成也。文献之成始而未成终者。并有待于今 王也。是帖之颁。即其一也。垂死贱臣。幸与于此。谨百拜而为之书。
年。一是揆也。万世之文献。复得其主。而治教将日新矣。区区褥蚁之愿。更望须臾无死。备见德化之成也。文献之成始而未成终者。并有待于今 王也。是帖之颁。即其一也。垂死贱臣。幸与于此。谨百拜而为之书。赵胤卿(万永),羲卿(寅永)清潭游轴跋
清潭洞壑之胜。实为三角之最。而始具氏居之。 孝庙初服。尤庵先生避胡啧。暂憩于此。近郭非乏幽隩。独以是为归。盖取西山之清也。旋复南归。留诗勒于洞门之崖。后为宰相别业。楼观特侈。而三渊先生亦尝寓居焉。诗揭楼额。清潭益重。余家距此二舍馀。而到老未能一游。内愧多矣。今观胤卿伯季之游轴。益自怅然久之。况玆七月既望。苏仙赤壁之馀。而岁则十一周矣。胤卿,羲卿之传家文学。可比眉山。不独后生之可畏。而湖上其故居也。乃舍之而就岩穴。其意益清矣。轴中士友。并又岳下之选也。相与竟夜唱酬。风流烂漫。文采照映。恨不使苏仙见之。彼独一箫客也。比此顾不冷寂哉。羲卿托余评批。老我岂能役哉。徒愧一饭之先也。然清潭之于苏仙。亦迂也。二先生之清风近。可师也。玆游可复使清潭重耶。书之为轴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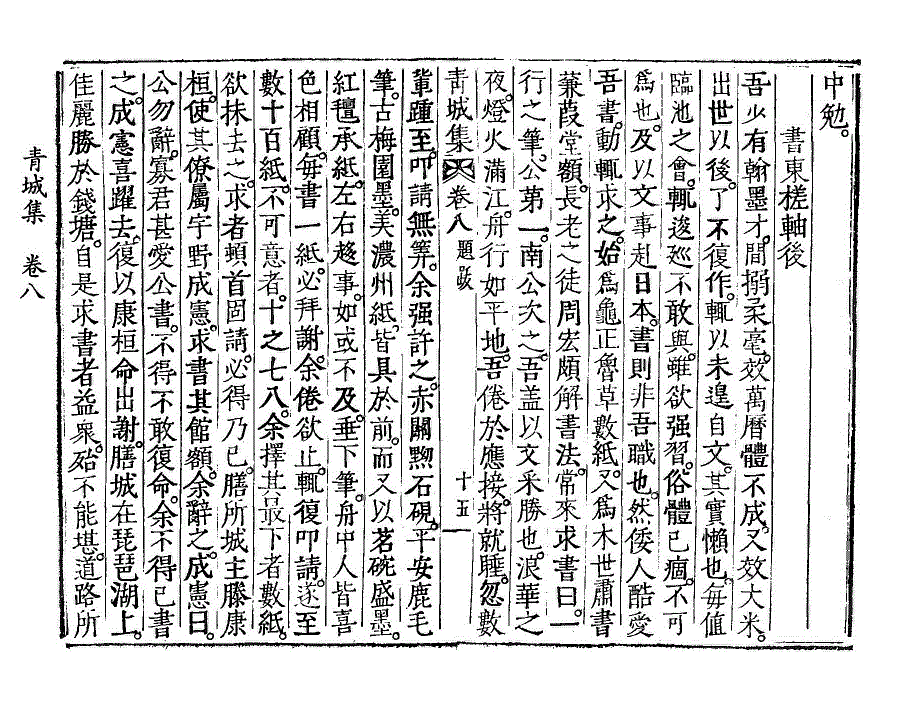 中勉。
中勉。书东槎轴后
吾少有翰墨才。间搦柔毫。效万历体不成。又效大米。出世以后。了不复作。辄以未遑自文。其实懒也。每值临池之会。辄逡巡不敢与。虽欲强习。俗体已痼。不可为也。及以文事赴日本。书则非吾职也。然倭人酷爱吾书。动辄求之。始为龟正鲁草数纸。又为木世肃书蒹葭堂额。长老之徒周宏颇解书法。常来求书曰。一行之笔。公第一。南公次之。吾盖以文采胜也。浪华之夜。灯火满江。舟行如平地。吾倦于应接。将就睡。忽数辈踵至。叩请无算。余强许之。赤关黝石砚。平安鹿毛笔。古梅园墨。美浓州纸。皆具于前。而又以茗碗盛墨。红毡承纸。左右趍事。如或不及。垂下笔。舟中人皆喜色相顾。每书一纸。必拜谢。余倦欲止。辄复叩请。遂至数十百纸。不可意者。十之七八。余择其最下者数纸。欲抹去之。求者顿首固请。必得乃已。膳所城主滕康桓。使其僚属宇野成宪。求书其馆额。余辞之。成宪曰。公勿辞。寡君甚爱公书。不得不敢复命。余不得已书之。成宪喜跃去。复以康桓命出谢。膳城在琵琶湖上。佳丽胜于钱塘。自是求书者益众。殆不能堪。道路所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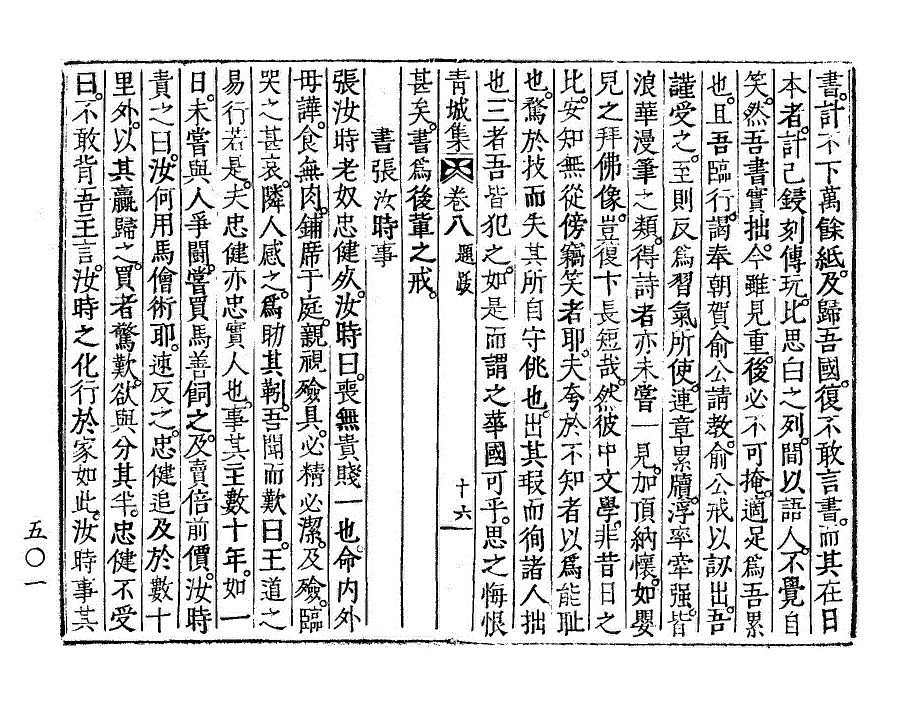 书。计不下万馀纸。及归吾国。复不敢言书。而其在日本者。计已锓刻传玩。比思白之列。间以语人。不觉自笑。然吾书实拙。今虽见重。后必不可掩。适足为吾累也。且吾临行。谒奉朝贺俞公请教。俞公戒以讱出。吾谨受之。至则反为习气所使。连章累牍。浮率牵强。皆浪华漫笔之类。得诗者亦未尝一见。加顶纳怀。如婴儿之拜佛像。岂复卞长短哉。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傍窃笑者耶。夫夸于不知者以为能耻也。骛于技而失其所自守佻也。出其瑕而徇诸人拙也。三者吾皆犯之。如是而谓之华国可乎。思之悔恨甚矣。书为后辈之戒。
书。计不下万馀纸。及归吾国。复不敢言书。而其在日本者。计已锓刻传玩。比思白之列。间以语人。不觉自笑。然吾书实拙。今虽见重。后必不可掩。适足为吾累也。且吾临行。谒奉朝贺俞公请教。俞公戒以讱出。吾谨受之。至则反为习气所使。连章累牍。浮率牵强。皆浪华漫笔之类。得诗者亦未尝一见。加顶纳怀。如婴儿之拜佛像。岂复卞长短哉。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傍窃笑者耶。夫夸于不知者以为能耻也。骛于技而失其所自守佻也。出其瑕而徇诸人拙也。三者吾皆犯之。如是而谓之华国可乎。思之悔恨甚矣。书为后辈之戒。书张汝时事
张汝时老奴忠健死。汝时曰。丧无贵贱一也。命内外毋哗。食无肉。铺席于庭。亲视殓具。必精必洁。及殓。临哭之甚哀。邻人感之。为助其靷。吾闻而叹曰。王道之易行若是。夫忠健亦忠实人也。事其主数十年。如一日。未尝与人争斗。尝买马善饲之。及卖倍前价。汝时责之曰。汝何用马侩术耶。速反之。忠健追及于数十里外。以其赢归之。买者惊叹。欲与分其半。忠健不受曰。不敢背吾主言。汝时之化行于家如此。汝时事其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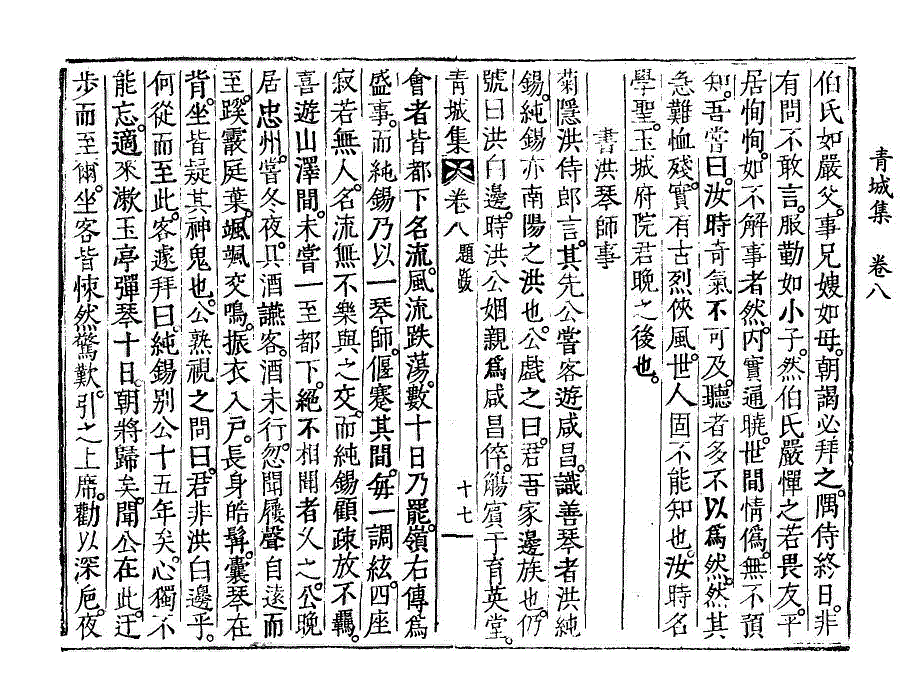 伯氏如严父。事兄嫂如母。朝谒必拜之。隅侍终日。非有问不敢言。服勤如小子。然伯氏严惮之若畏友。平居恂恂。如不解事者然。内实通晓。世间情伪。无不预知。吾尝曰。汝时奇气不可及。听者多不以为然。然其急难恤残。实有古烈侠风。世人固不能知也。汝时名学圣。玉城府院君晚之后也。
伯氏如严父。事兄嫂如母。朝谒必拜之。隅侍终日。非有问不敢言。服勤如小子。然伯氏严惮之若畏友。平居恂恂。如不解事者然。内实通晓。世间情伪。无不预知。吾尝曰。汝时奇气不可及。听者多不以为然。然其急难恤残。实有古烈侠风。世人固不能知也。汝时名学圣。玉城府院君晚之后也。书洪琴师事
菊隐洪侍郎言。其先公尝客游咸昌。识善琴者洪纯锡。纯锡亦南阳之洪也。公戏之曰。君吾家边族也。仍号曰洪白边。时洪公姻亲为咸昌倅。觞宾于育英堂。会者皆都下名流。风流跌荡。数十日乃罢。岭右传为盛事。而纯锡乃以一琴师。偃蹇其间。每一调弦。四座寂若无人。名流无不乐与之交。而纯锡顾疏放不羁。喜游山泽间。未尝一至都下。绝不相闻者久之。公晚居忠州。尝冬夜。具酒宴客。酒未行。忽闻屦声自远而至。蹊霰庭叶。飒飒交鸣。振衣入户。长身皓髯。囊琴在背。坐皆疑其神鬼也。公熟视之问曰。君非洪白边乎。何从而至此。客遽拜曰。纯锡别公十五年矣。心独不能忘。适来漱玉亭弹琴十日。朝将归矣。闻公在此。迂步而至尔。坐客皆悚然惊叹。引之上席。劝以深卮。夜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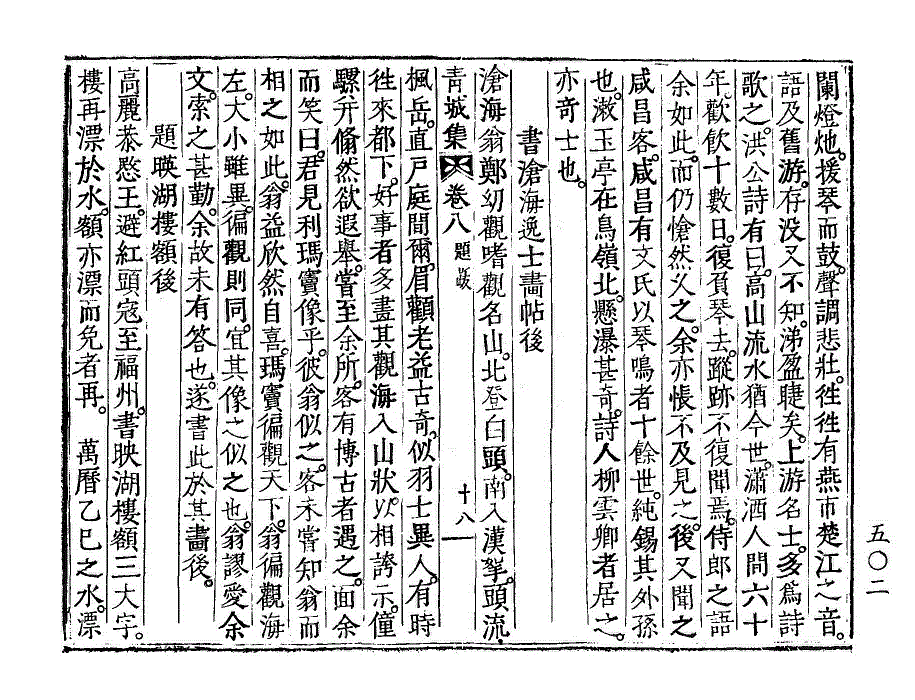 阑灯灺。援琴而鼓。声调悲壮。往往有燕市楚江之音。语及旧游。存没又不知。涕盈睫矣。上游名士。多为诗歌之。洪公诗有曰。高山流水犹今世。潇洒人间六十年。欢饮十数日。复负琴去。踪迹不复闻焉。侍郎之语余如此。而仍怆然久之。余亦怅不及见之。后又闻之咸昌客。咸昌有文氏以琴鸣者十馀世。纯锡其外孙也。漱玉亭在鸟岭北。悬瀑甚奇。诗人柳云卿者居之。亦奇士也。
阑灯灺。援琴而鼓。声调悲壮。往往有燕市楚江之音。语及旧游。存没又不知。涕盈睫矣。上游名士。多为诗歌之。洪公诗有曰。高山流水犹今世。潇洒人间六十年。欢饮十数日。复负琴去。踪迹不复闻焉。侍郎之语余如此。而仍怆然久之。余亦怅不及见之。后又闻之咸昌客。咸昌有文氏以琴鸣者十馀世。纯锡其外孙也。漱玉亭在鸟岭北。悬瀑甚奇。诗人柳云卿者居之。亦奇士也。书沧海逸士画帖后
沧海翁郑幼观嗜观名山。北登白头。南入汉挐。头流,枫岳。直户庭间尔。眉颧老益古奇。似羽士异人。有时往来都下。好事者多画其观海入山状。以相誇示。僮骡并翛然欲遐举。尝至余所。客有博古者遇之。面余而笑曰。君见利玛窦像乎。彼翁似之。客未尝知翁而相之如此。翁益欣然自喜。玛窦遍观天下。翁遍观海左。大小虽异。遍观则同。宜其像之似之也。翁谬爱余文。索之甚勤。余故未有答也。遂书此于其画后。
题映湖楼额后
高丽恭悯王。避红头寇至福州。书映湖楼额三大字。楼再漂于水。额亦漂而免者再。 万历乙巳之水。漂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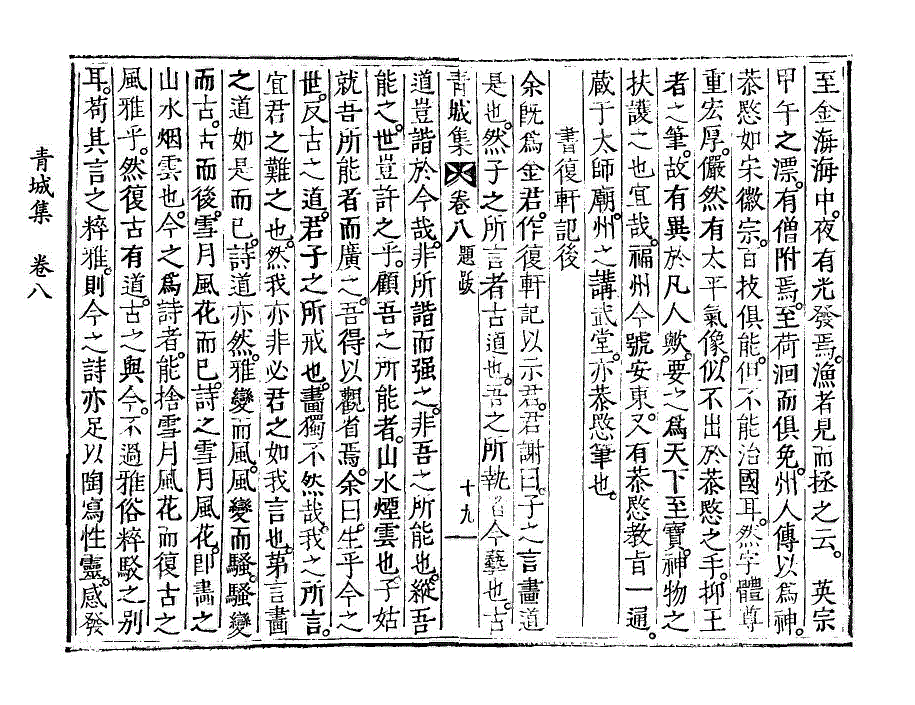 至金海海中。夜有光发焉。渔者见而拯之云。 英宗甲午之漂。有僧附焉。至荷洄而俱免。州人传以为神。恭悯如宋徽宗。百技俱能。但不能治国耳。然字体尊重宏厚。俨然有太平气像。似不出于恭悯之手。抑王者之笔。故有异于凡人欤。要之为天下至宝。神物之扶护之也宜哉。福州今号安东。又有恭悯教旨一通。藏于太师庙。州之讲武堂。亦恭悯笔也。
至金海海中。夜有光发焉。渔者见而拯之云。 英宗甲午之漂。有僧附焉。至荷洄而俱免。州人传以为神。恭悯如宋徽宗。百技俱能。但不能治国耳。然字体尊重宏厚。俨然有太平气像。似不出于恭悯之手。抑王者之笔。故有异于凡人欤。要之为天下至宝。神物之扶护之也宜哉。福州今号安东。又有恭悯教旨一通。藏于太师庙。州之讲武堂。亦恭悯笔也。书复轩记后
余既为金君。作复轩记以示君。君谢曰。子之言画道是也。然子之所言者古道也。吾之所执者今艺也。古道岂谐于今哉。非所谐而强之。非吾之所能也。纵吾能之。世岂许之乎。顾吾之所能者。山水烟云也。子姑就吾所能者而广之。吾得以观省焉。余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君子之所戒也。画独不然哉。我之所言。宜君之难之也。然我亦非必君之如我言也。第言画之道如是而已。诗道亦然。雅变而风。风变而骚。骚变而古。古而后。雪月风花而已。诗之雪月风花。即画之山水烟云也。今之为诗者。能舍雪月风花而复古之风雅乎。然复古有道。古之与今。不过雅俗粹驳之别耳。苟其言之粹雅。则今之诗亦足以陶写性灵。感发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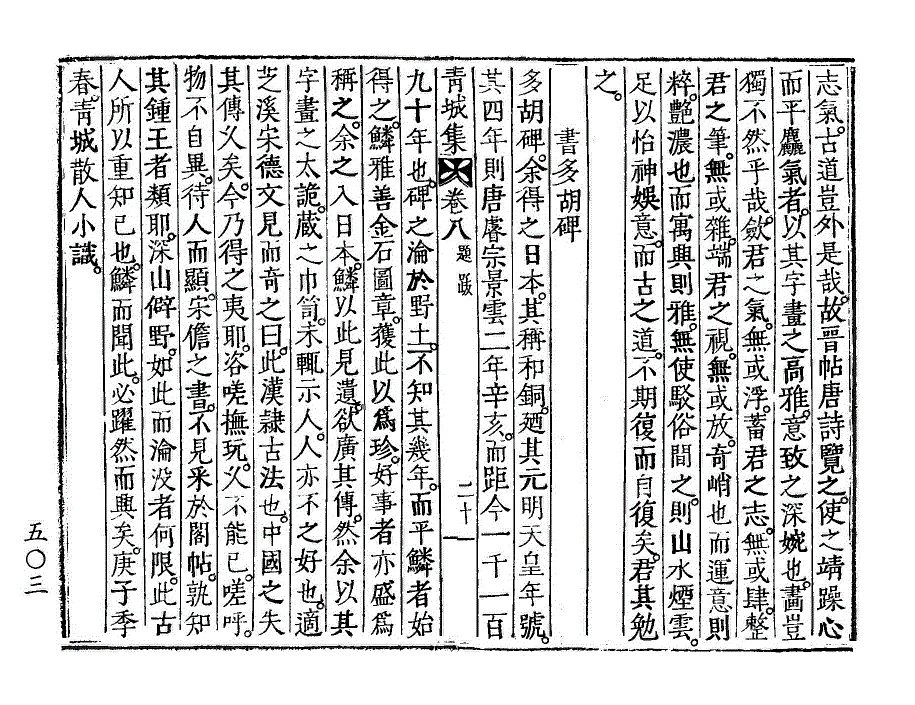 志气。古道岂外是哉。故晋帖唐诗览之。使之靖躁心而平粗气者。以其字画之高雅。意致之深婉也。画岂独不然乎哉。敛君之气。无或浮。蓄君之志。无或肆。整君之笔。无或杂。端君之视。无或放。奇峭也而运意则粹。艳浓也而寓兴则雅。无使驳俗间之。则山水烟云。足以怡神娱意。而古之道。不期复而自复矣。君其勉之。
志气。古道岂外是哉。故晋帖唐诗览之。使之靖躁心而平粗气者。以其字画之高雅。意致之深婉也。画岂独不然乎哉。敛君之气。无或浮。蓄君之志。无或肆。整君之笔。无或杂。端君之视。无或放。奇峭也而运意则粹。艳浓也而寓兴则雅。无使驳俗间之。则山水烟云。足以怡神娱意。而古之道。不期复而自复矣。君其勉之。书多胡碑
多胡碑。余得之日本。其称和铜。乃其元明天皇年号。其四年则唐睿宗景云二年辛亥。而距今一千一百九十年也。碑之沦于野土。不知其几年。而平鳞者始得之。鳞雅善金石图章。获此以为珍。好事者亦盛为称之。余之入日本。鳞以此见遗。欲广其传。然余以其字画之太诡。藏之巾笥。未辄示人。人亦不之好也。适芝溪宋德文见而奇之曰。此汉隶古法也。中国之失其传久矣。今乃得之夷耶。咨嗟抚玩。久不能已。嗟呼。物不自异。待人而显。宋儋之书。不见采于阁帖。孰知其钟王者类耶。深山僻野。如此而沦没者何限。此古人所以重知己也。鳞而闻此。必跃然而兴矣。庚子季春。青城散人小识。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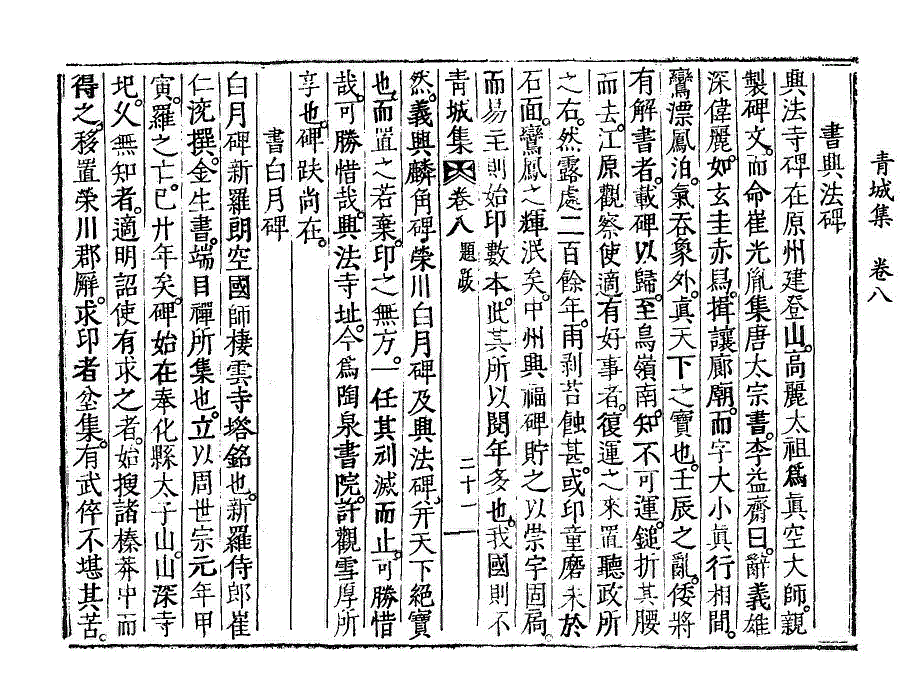 书兴法碑
书兴法碑兴法寺碑在原州建登山。高丽太祖为真空大师。亲制碑文。而命崔光胤集唐太宗书。李益斋曰。辞义雄深伟丽。如玄圭赤舄。揖让廊庙。而字大小真行相间。鸾漂凤泊。气吞象外。真天下之宝也。壬辰之乱。倭将有解书者。载碑以归。至鸟岭南。知不可运。锤折其腰而去。江原观察使适有好事者。复运之来置听政所之右。然露处二百馀年。雨剥苔蚀甚。或印童磨朱于石面。鸾凤之辉泯矣。中州兴福碑贮之以崇宇固扃。而易主则始印数本。此其所以阅年多也。我国则不然。义兴麟角碑,荣川白月碑及兴法碑。并天下绝宝也。而置之若弃。印之无方。一任其刓灭而止。可胜惜哉。可胜惜哉。兴法寺址。今为陶泉书院。许观雪厚所享也。碑趺尚在。
书白月碑
白月碑新罗朗空国师栖云寺塔铭也。新罗侍郎崔仁渷撰。金生书。端目禅所集也。立以周世宗元年甲寅。罗之亡。已廿年矣。碑始在奉化县太子山。山深寺圮。久无知者。适明诏使有求之者。始搜诸榛莽中而得之。移置荣川郡廨。求印者坌集。有武倅不堪其苦。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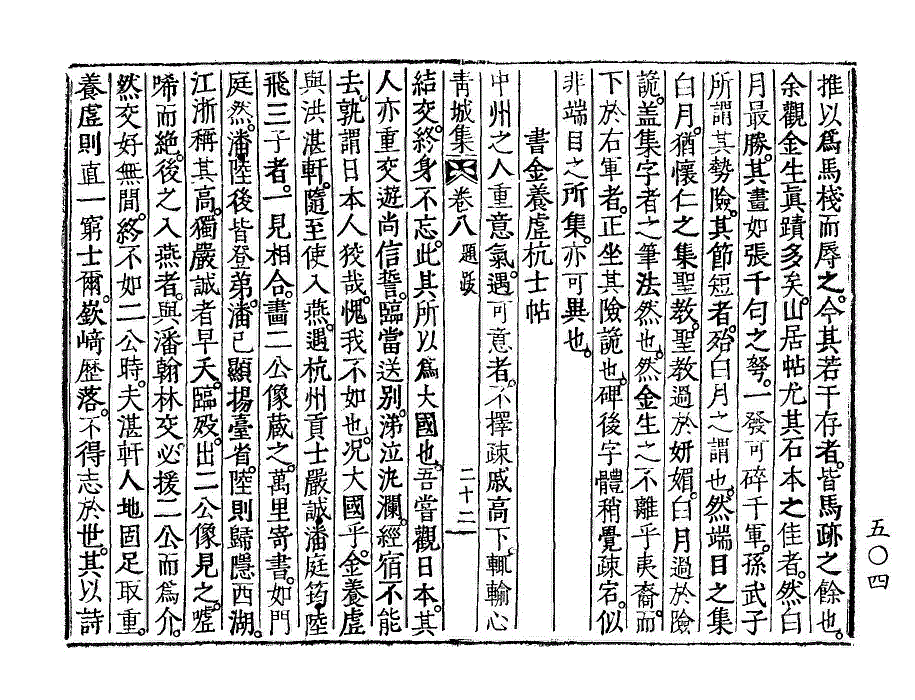 推以为马栈而辱之。今其若干存者。皆马迹之馀也。余观金生真迹多矣。山居帖尤其石本之佳者。然白月最胜。其画如张千匀之弩。一发可碎千军。孙武子所谓其势险。其节短者。殆白月之谓也。然端目之集白月。犹怀仁之集圣教。圣教过于妍媚。白月过于险诡。盖集字者之笔法然也。然金生之不离乎夷裔。而下于右军者。正坐其险诡也。碑后字体稍觉疏宕。似非端目之所集。亦可异也。
推以为马栈而辱之。今其若干存者。皆马迹之馀也。余观金生真迹多矣。山居帖尤其石本之佳者。然白月最胜。其画如张千匀之弩。一发可碎千军。孙武子所谓其势险。其节短者。殆白月之谓也。然端目之集白月。犹怀仁之集圣教。圣教过于妍媚。白月过于险诡。盖集字者之笔法然也。然金生之不离乎夷裔。而下于右军者。正坐其险诡也。碑后字体稍觉疏宕。似非端目之所集。亦可异也。书金养虚杭士帖
中州之人重意气。遇可意者。不择疏戚高下。辄输心结交。终身不忘。此其所以为大国也。吾尝观日本。其人亦重交游尚信誓。临当送别。涕泣汍澜。经宿不能去。孰谓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况大国乎。金养虚与洪湛轩。随至使入燕。遇杭州贡士严诚,潘庭筠,陆飞三子者。一见相合。画二公像藏之。万里寄书。如门庭然。潘,陆后皆登第。潘已显扬台省。陆则归隐西湖。江浙称其高。独严诚者早夭。临殁。出二公像见之。嘘唏而绝。后之入燕者。与潘翰林交。必援二公而为介。然交好无间。终不如二公时。夫湛轩人地固足取重。养虚则直一穷士尔。嵚崎历落。不得志于世。其以诗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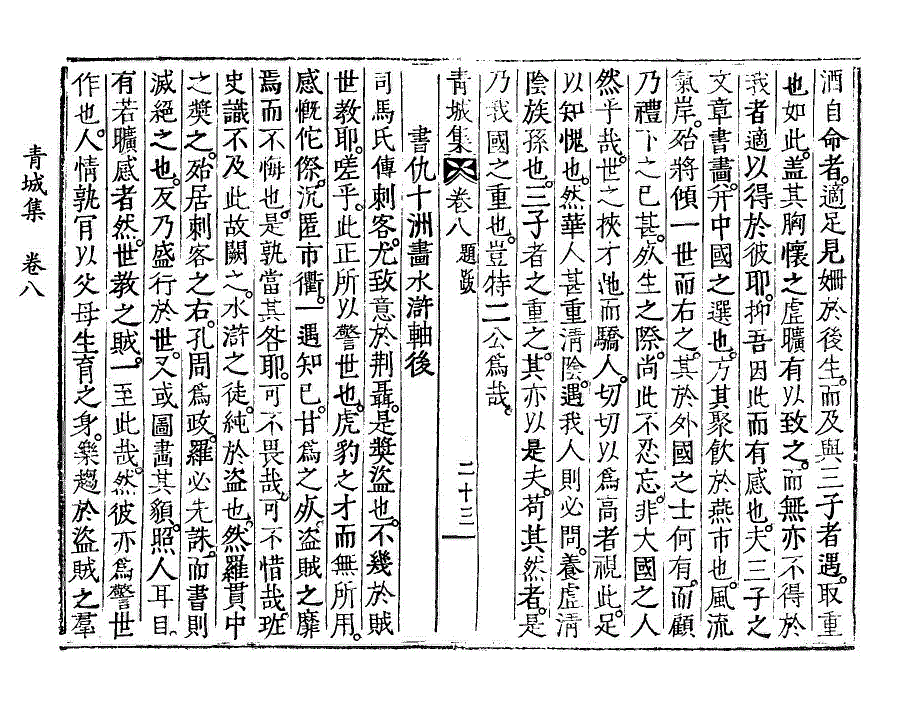 酒自命者。适足见姗于后生。而及与三子者遇。取重也如此。盖其胸怀之虚旷有以致之。而无亦不得于我者适以得于彼耶。抑吾因此而有感也。夫三子之文章书画。并中国之选也。方其聚饮于燕市也。风流气岸。殆将倾一世而右之。其于外国之士何有。而顾乃礼下之已甚。死生之际。尚此不忍忘。非大国之人然乎哉。世之挟才地而骄人。切切以为高者视此。足以知愧也。然华人甚重清阴。遇我人则必问。养虚清阴族孙也。三子者之重之。其亦以是夫。苟其然者。是乃我国之重也。岂特二公为哉。
酒自命者。适足见姗于后生。而及与三子者遇。取重也如此。盖其胸怀之虚旷有以致之。而无亦不得于我者适以得于彼耶。抑吾因此而有感也。夫三子之文章书画。并中国之选也。方其聚饮于燕市也。风流气岸。殆将倾一世而右之。其于外国之士何有。而顾乃礼下之已甚。死生之际。尚此不忍忘。非大国之人然乎哉。世之挟才地而骄人。切切以为高者视此。足以知愧也。然华人甚重清阴。遇我人则必问。养虚清阴族孙也。三子者之重之。其亦以是夫。苟其然者。是乃我国之重也。岂特二公为哉。书仇十洲画水浒轴后
司马氏传刺客。尤致意于荆聂。是奖盗也。不几于贼世教耶。嗟乎。此正所以警世也。虎豹之才而无所用。感慨佗傺。沉匿市衢。一遇知己。甘为之死。盗贼之靡焉而不悔也。是孰当其咎耶。可不畏哉。可不惜哉。班史识不及此故阙之。水浒之徒。纯于盗也。然罗贯中之奖之。殆居刺客之右。孔周为政。罗必先诛。而书则灭绝之也。反乃盛行于世。又或图画其䫉。照人耳目。有若旷感者然。世教之贼。一至此哉。然彼亦为警世作也。人情孰肯以父母生育之身。乐趋于盗贼之群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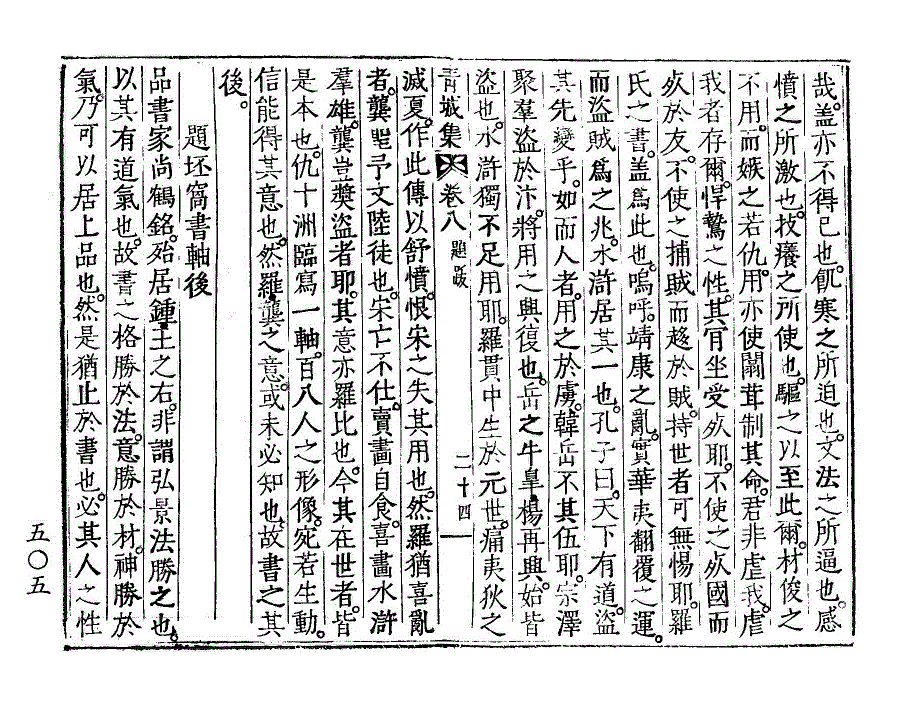 哉。盖亦不得已也。饥寒之所迫也。文法之所逼也。感愤之所激也。技痒之所使也。驱之以至此尔。材俊之不用。而嫉之若仇。用亦使阘茸制其命。君非虐我。虐我者存尔。悍鸷之性。其肯坐受死耶。不使之死国而死于友。不使之捕贼而趍于贼。持世者可无惕耶。罗氏之书。盖为此也。呜呼。靖康之乱。实华夷翻覆之运。而盗贼为之兆。水浒居其一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如而人者。用之于虏。韩岳不其伍耶。宗泽聚群盗于汴。将用之兴复也。岳之牛皋,杨再兴。始皆盗也。水浒独不足用耶。罗贯中生于元世。痛夷狄之灭夏。作此传以舒愤。恨宋之失其用也。然罗犹喜乱者。龚圣予文陆徒也。宋亡不仕。卖画自食。喜画水浒群雄。龚岂奖盗者耶。其意亦罗比也。今其在世者。皆是本也。仇十洲临写一轴。百八人之形像。宛若生动。信能得其意也。然罗,龚之意。或未必知也。故书之其后。
哉。盖亦不得已也。饥寒之所迫也。文法之所逼也。感愤之所激也。技痒之所使也。驱之以至此尔。材俊之不用。而嫉之若仇。用亦使阘茸制其命。君非虐我。虐我者存尔。悍鸷之性。其肯坐受死耶。不使之死国而死于友。不使之捕贼而趍于贼。持世者可无惕耶。罗氏之书。盖为此也。呜呼。靖康之乱。实华夷翻覆之运。而盗贼为之兆。水浒居其一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如而人者。用之于虏。韩岳不其伍耶。宗泽聚群盗于汴。将用之兴复也。岳之牛皋,杨再兴。始皆盗也。水浒独不足用耶。罗贯中生于元世。痛夷狄之灭夏。作此传以舒愤。恨宋之失其用也。然罗犹喜乱者。龚圣予文陆徒也。宋亡不仕。卖画自食。喜画水浒群雄。龚岂奖盗者耶。其意亦罗比也。今其在世者。皆是本也。仇十洲临写一轴。百八人之形像。宛若生动。信能得其意也。然罗,龚之意。或未必知也。故书之其后。题坯窝书轴后
品书家尚鹤铭。殆居钟,王之右。非谓弘景法胜之也。以其有道气也。故书之格胜于法。意胜于材。神胜于气。乃可以居上品也。然是犹止于书也。必其人之性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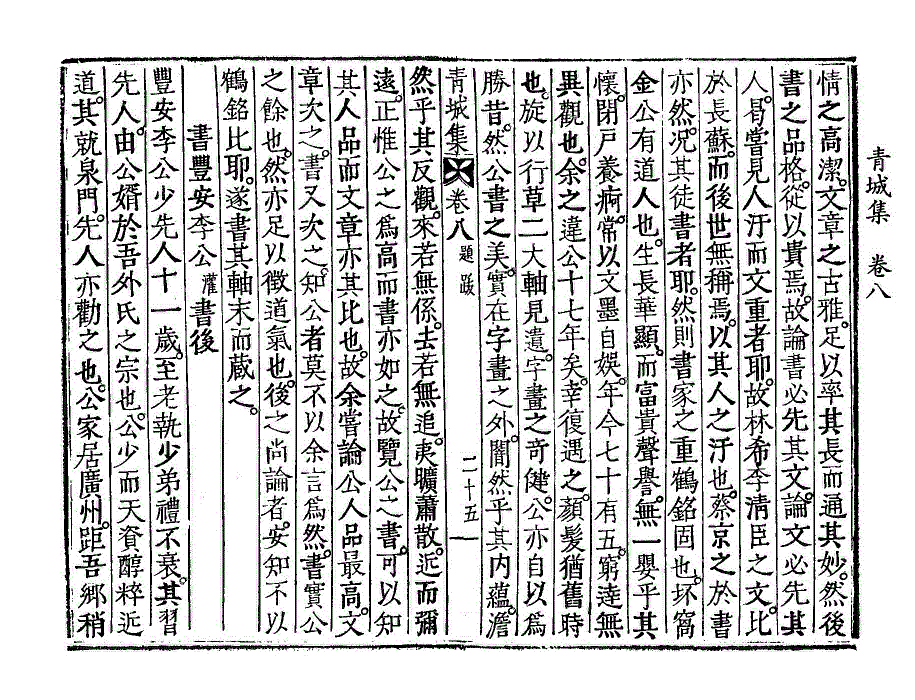 情之高洁。文章之古雅。足以率其长而通其妙。然后书之品格。从以贵焉。故论书必先其文。论文必先其人。曷尝见人污而文重者耶。故林希,李清臣之文。比于长苏。而后世无称焉。以其人之污也。蔡京之于书亦然。况其徒书者耶。然则书家之重鹤铭固也。坏窝金公有道人也。生长华显。而富贵声誉。无一婴乎其怀。闭户养痾。常以文墨自娱。年今七十有五。穷达无异观也。余之违公十七年矣。幸复遇之。颜发犹旧时也。旋以行草二大轴见遗。字画之奇健。公亦自以为胜昔。然公书之美。实在字画之外。闇然乎其内蕴。澹然乎其反观。来若无系。去若无追。夷旷萧散。近而弥远。正惟公之为高而书亦如之。故览公之书。可以知其人品而文章亦其比也。故余尝论公人品最高。文章次之。书又次之。知公者莫不以余言为然。书实公之馀也。然亦足以徵道气也。后之尚论者。安知不以鹤铭比耶。遂书其轴末而藏之。
情之高洁。文章之古雅。足以率其长而通其妙。然后书之品格。从以贵焉。故论书必先其文。论文必先其人。曷尝见人污而文重者耶。故林希,李清臣之文。比于长苏。而后世无称焉。以其人之污也。蔡京之于书亦然。况其徒书者耶。然则书家之重鹤铭固也。坏窝金公有道人也。生长华显。而富贵声誉。无一婴乎其怀。闭户养痾。常以文墨自娱。年今七十有五。穷达无异观也。余之违公十七年矣。幸复遇之。颜发犹旧时也。旋以行草二大轴见遗。字画之奇健。公亦自以为胜昔。然公书之美。实在字画之外。闇然乎其内蕴。澹然乎其反观。来若无系。去若无追。夷旷萧散。近而弥远。正惟公之为高而书亦如之。故览公之书。可以知其人品而文章亦其比也。故余尝论公人品最高。文章次之。书又次之。知公者莫不以余言为然。书实公之馀也。然亦足以徵道气也。后之尚论者。安知不以鹤铭比耶。遂书其轴末而藏之。书丰安李公(灌)书后
丰安李公少先人十一岁。至老执少弟礼不衰。其习先人。由公婿于吾外氏之宗也。公少而天资醇粹近道。其就泉门。先人亦劝之也。公家居广州。距吾乡稍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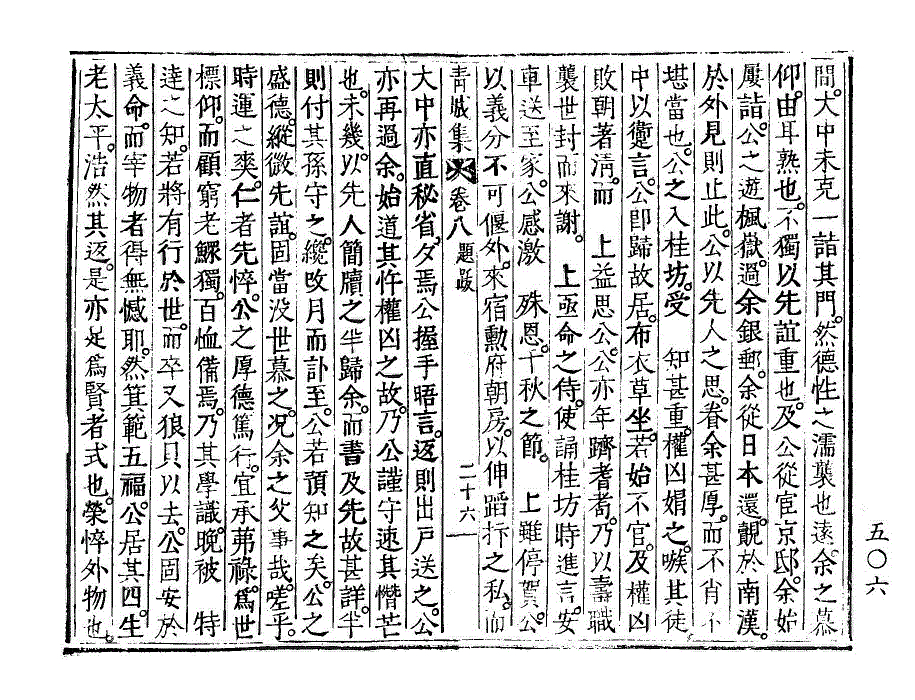 间。大中未克一诣其门。然德性之濡袭也远。余之慕仰。由耳熟也。不独以先谊重也。及公从宦京邸。余始屡诣。公之游枫岳。过余银邮。余从日本还。觌于南汉。于外见则止此。公以先人之思。眷余甚厚。而不肖不堪当也。公之入桂坊。受 知甚重。权凶媢之。嗾其徒中以躗言。公即归故居。布衣草坐。若始不官。及权凶败朝著清。而 上益思公。公亦年跻耆耇。乃以寿职袭世封而来谢。 上亟命之侍。使诵桂坊时进言。安车送至家。公感激 殊恩。千秋之节。 上虽停贺。公以义分不可偃外。来宿勋府朝房。以伸蹈抃之私。而大中亦直秘省。夕焉公握手晤言。返则出户送之。公亦再过余。始道其忤权凶之故。乃公谨守速其憯芒也。未几。以先人简牍之半归余。而书及先故甚详。半则付其孙守之。才改月而讣至。公若预知之矣。公之盛德。纵微先谊。固当没世慕之。况余之父事哉。嗟乎。时运之爽。仁者先悴。公之厚德笃行。宜承茀禄。为世标仰。而顾穷老鳏独。百恤备焉。乃其学识。晚被 特达之知。若将有行于世。而卒又狼贝以去。公固安于义命。而宰物者得无憾耶。然箕范五福。公居其四。生老太平。浩然其返。是亦足为贤者式也。荣悴外物也。
间。大中未克一诣其门。然德性之濡袭也远。余之慕仰。由耳熟也。不独以先谊重也。及公从宦京邸。余始屡诣。公之游枫岳。过余银邮。余从日本还。觌于南汉。于外见则止此。公以先人之思。眷余甚厚。而不肖不堪当也。公之入桂坊。受 知甚重。权凶媢之。嗾其徒中以躗言。公即归故居。布衣草坐。若始不官。及权凶败朝著清。而 上益思公。公亦年跻耆耇。乃以寿职袭世封而来谢。 上亟命之侍。使诵桂坊时进言。安车送至家。公感激 殊恩。千秋之节。 上虽停贺。公以义分不可偃外。来宿勋府朝房。以伸蹈抃之私。而大中亦直秘省。夕焉公握手晤言。返则出户送之。公亦再过余。始道其忤权凶之故。乃公谨守速其憯芒也。未几。以先人简牍之半归余。而书及先故甚详。半则付其孙守之。才改月而讣至。公若预知之矣。公之盛德。纵微先谊。固当没世慕之。况余之父事哉。嗟乎。时运之爽。仁者先悴。公之厚德笃行。宜承茀禄。为世标仰。而顾穷老鳏独。百恤备焉。乃其学识。晚被 特达之知。若将有行于世。而卒又狼贝以去。公固安于义命。而宰物者得无憾耶。然箕范五福。公居其四。生老太平。浩然其返。是亦足为贤者式也。荣悴外物也。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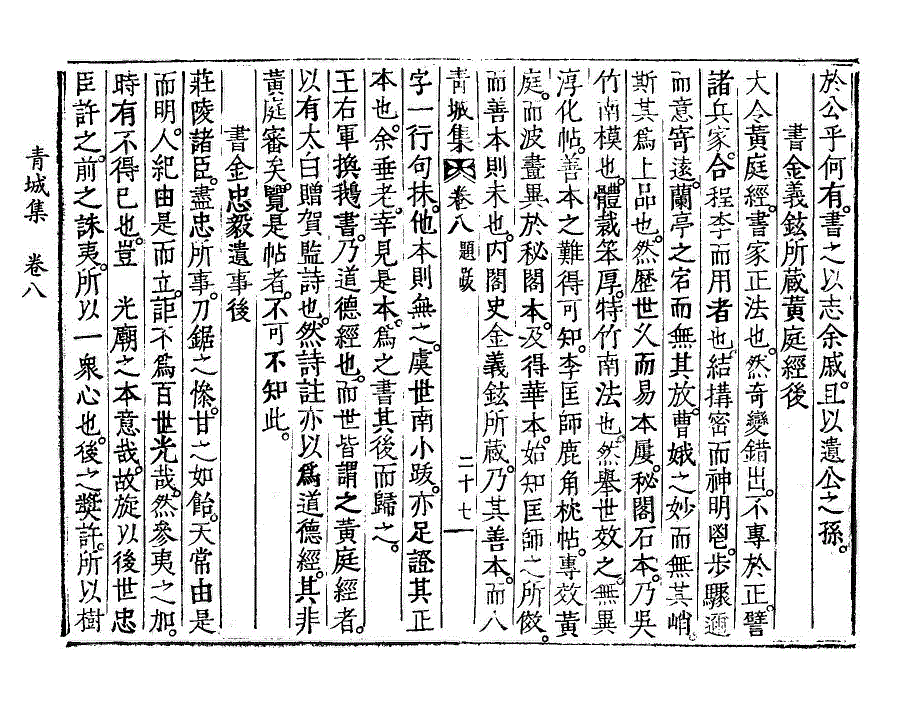 于公乎何有。书之以志余戚。且以遗公之孙。
于公乎何有。书之以志余戚。且以遗公之孙。书金义铉所藏黄庭经后
大令黄庭经。书家正法也。然奇变错出。不专于正。譬诸兵家。合程李而用者也。结搆密而神明鬯。步骤迩而意寄远。兰亭之宕而无其放。曹娥之妙而无其峭。斯其为上品也。然历世久而易本屡。秘阁石本。乃吴竹南模也。体裁笨厚。特竹南法也。然举世效之。无异淳化帖。善本之难得可知。李匡师鹿角枕帖。专效黄庭。而波画异于秘阁本。及得华本。始知匡师之所效。而善本则未也。内阁史金义铉所藏。乃其善本。而人字一行句抹。他本则无之。虞世南小跋。亦足證其正本也。余垂老。幸见是本。为之书其后而归之。
王右军换鹅书。乃道德经也。而世皆谓之黄庭经者。以有太白赠贺监诗也。然诗注亦以为道德经。其非黄庭审矣。览是帖者。不可不知此。
书金忠毅遗事后
庄陵诸臣。尽忠所事。刀锯之惨。甘之如饴。天常由是而明。人纪由是而立。讵不为百世光哉。然参夷之加。时有不得已也。岂 光庙之本意哉。故旋以后世忠臣许之。前之诛夷。所以一众心也。后之奖许。所以树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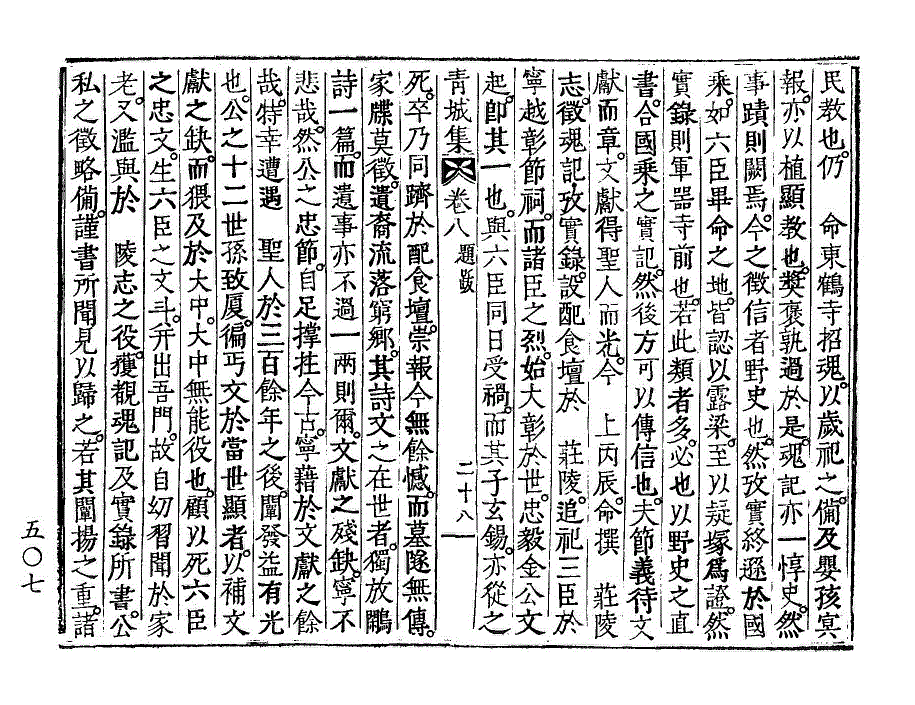 民教也。仍 命东鹤寺招魂。以岁祀之。备及婴孩冥报。亦以植显教也。奖褒孰过于是。魂记亦一惇史。然事迹则阙焉。今之徵信者野史也。然考实终逊于国乘。如六臣毕命之地。皆认以露梁。至以疑冢为證。然实录则军器寺前也。若此类者多。必也以野史之直书。合国乘之实记。然后方可以传信也。夫节义待文献而章。文献得圣人而光。今 上丙辰。命撰 庄陵志。徵魂记,考实录。设配食坛于 庄陵。追祀三臣于宁越彰节祠。而诸臣之烈。始大彰于世。忠毅金公文起。即其一也。与六臣同日受祸。而其子玄锡。亦从之死。卒乃同跻于配食坛。崇报今无馀憾。而墓隧无传。家牒莫徵。遗裔流落穷乡。其诗文之在世者。独放鹇诗一篇。而遗事亦不过一两则尔。文献之残缺。宁不悲哉。然公之忠节。自足撑拄今古。宁藉于文献之馀哉。特幸遭遇 圣人于三百馀年之后。阐发益有光也。公之十二世孙致厦。遍丐文于当世显者。以补文献之缺。而猥及于大中。大中无能役也。顾以死六臣之忠文。生六臣之文斗。并出吾门。故自幼习闻于家老。又滥与于 陵志之役。获睹魂记及实录所书。公私之徵略备。谨书所闻见以归之。若其阐扬之重。诸
民教也。仍 命东鹤寺招魂。以岁祀之。备及婴孩冥报。亦以植显教也。奖褒孰过于是。魂记亦一惇史。然事迹则阙焉。今之徵信者野史也。然考实终逊于国乘。如六臣毕命之地。皆认以露梁。至以疑冢为證。然实录则军器寺前也。若此类者多。必也以野史之直书。合国乘之实记。然后方可以传信也。夫节义待文献而章。文献得圣人而光。今 上丙辰。命撰 庄陵志。徵魂记,考实录。设配食坛于 庄陵。追祀三臣于宁越彰节祠。而诸臣之烈。始大彰于世。忠毅金公文起。即其一也。与六臣同日受祸。而其子玄锡。亦从之死。卒乃同跻于配食坛。崇报今无馀憾。而墓隧无传。家牒莫徵。遗裔流落穷乡。其诗文之在世者。独放鹇诗一篇。而遗事亦不过一两则尔。文献之残缺。宁不悲哉。然公之忠节。自足撑拄今古。宁藉于文献之馀哉。特幸遭遇 圣人于三百馀年之后。阐发益有光也。公之十二世孙致厦。遍丐文于当世显者。以补文献之缺。而猥及于大中。大中无能役也。顾以死六臣之忠文。生六臣之文斗。并出吾门。故自幼习闻于家老。又滥与于 陵志之役。获睹魂记及实录所书。公私之徵略备。谨书所闻见以归之。若其阐扬之重。诸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8H 页
 公之诗文在。
公之诗文在。书俞氏墓碣后
南秋江六臣传。以忠穆俞公为抱川人。海东名臣录亦然。然公素居抱川。书岂因其居欤。杞溪俞氏以公书诸其谱。亦未有信迹也。 英宗丙寅。公之遗墟碑始立。吾先子实为之倡也。于是公之傍孙居抱川者始出。乃公兄应信之后也。世居抱之东面。家牒郡籍。皆以抱为姓贯。然亦无信迹。杞抱等传疑也。盖其祸后。危踪窜匿。旧籍泯灭。莫得以考信也。君子之悲慨。岂独在俞氏哉。今 上戊午。东面之二碣见。一俞祯立墓也。一杨世显妻俞氏也。皆贯抱川而字独完。抱之有俞姓审矣。忠穆之贯抱。不足以徵信耶。杞谱徒引重也。荒原断碣。始判数百年之疑。幽隐固有待而发也。今 上褒奖节义。迥出千圣。六臣之崇报。殆无馀憾。而二碣出焉。文献与有助也。不亦为吾乡之光耶。余抱人也。故备书之。以待掌故之采。抑吾因是而别有感也。节义虽炳。非文献则莫显。夫露梁之冢。与秋江之传。同是六臣。而其一则异。冢则成忠肃。传则柳忠景也。忠肃之烈。忠穆比也。何逊于忠景。而露梁之祀。乃反让之。传为之主也。鲁恩故居。亦别祀也。吾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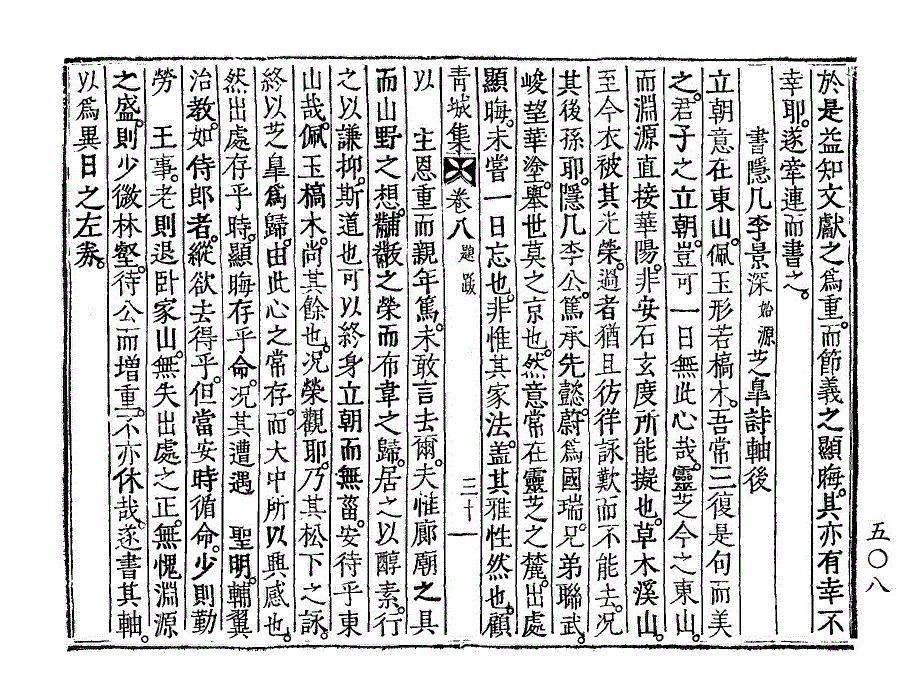 于是益知文献之为重。而节义之显晦。其亦有幸不幸耶。遂牵连而书之。
于是益知文献之为重。而节义之显晦。其亦有幸不幸耶。遂牵连而书之。书隐几李景深(始源)芝皋诗轴后
立朝意在东山。佩玉形若槁木。吾常三复是句而美之。君子之立朝。岂可一日无此心哉。灵芝今之东山。而渊源直接华阳。非安石玄度所能拟也。草木溪山。至今衣被其光荣。过者犹且彷徉咏叹而不能去。况其后孙耶。隐几李公。笃承先懿。蔚为国瑞。兄弟联武。峻望华涂。举世莫之京也。然意常在灵芝之麓。出处显晦。未尝一日忘也。非惟其家法。盖其雅性然也。顾以 主恩重而亲年笃。未敢言去尔。夫惟廊庙之具而山野之想。黼黻之荣而布韦之归。居之以醇素。行之以谦抑。斯道也可以终身立朝而无菑。安待乎东山哉。佩玉槁木。尚其馀也。况荣观耶。乃其松下之咏。终以芝皋为归。由此心之常存。而大中所以兴感也。然出处存乎时。显晦存乎命。况其遭遇 圣明。辅翼治教。如侍郎者。纵欲去得乎。但当安时循命。少则勤劳 王事。老则退卧家山。无失出处之正。无愧渊源之盛。则少微林壑。待公而增重。不亦休哉。遂书其轴。以为异日之左券。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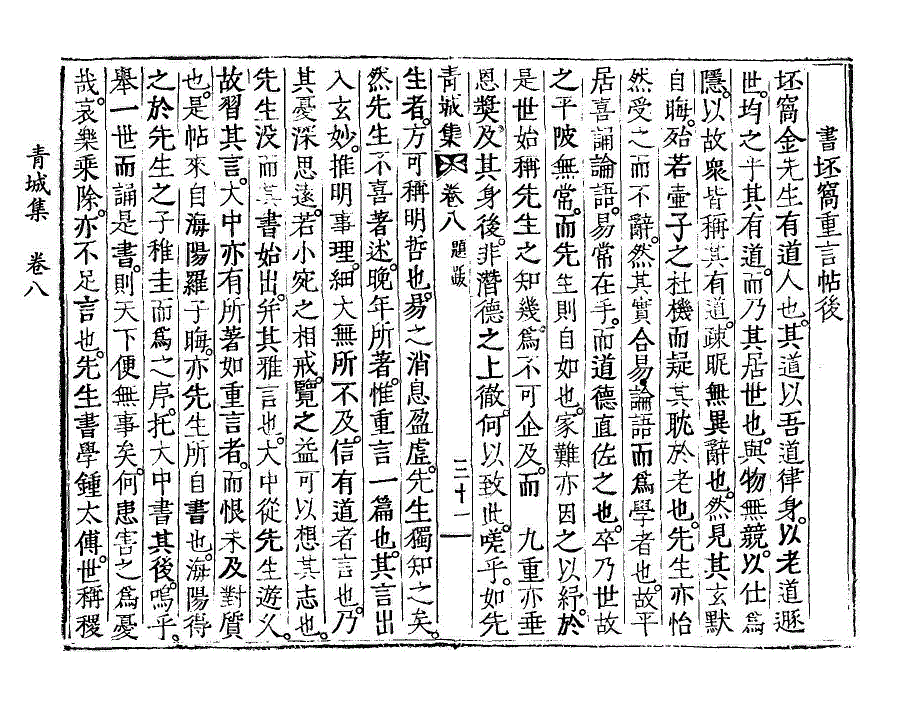 书坯窝重言帖后
书坯窝重言帖后坯窝金先生有道人也。其道以吾道律身。以老道遁世。均之乎其有道。而乃其居世也。与物无竞。以仕为隐。以故众皆称其有道。疏昵无异辞也。然见其玄默自晦。殆若壶子之杜机而疑其耽于老也。先生亦怡然受之而不辞。然其实合易,论语而为学者也。故平居喜诵论语。易常在手。而道德直佐之也。卒乃世故之平陂无常。而先生则自如也。家难亦因之以纾。于是世始称先生之知几。为不可企及。而 九重亦垂恩奖。及其身后。非潜德之上彻。何以致此。嗟乎。如先生者。方可称明哲也。易之消息盈虚。先生独知之矣。然先生不喜著述。晚年所著。惟重言一篇也。其言出入玄妙。推明事理。细大无所不及。信有道者言也。乃其忧深思远。若小宛之相戒。览之益可以想其志也。先生没而其书始出。并其雅言也。大中从先生游久。故习其言。大中亦有所著如重言者。而恨未及对质也。是帖来自海阳罗子晦。亦先生所自书也。海阳得之于先生之子稚圭而为之序。托大中书其后。呜乎。举一世而诵是书。则天下便无事矣。何患害之为忧哉。哀乐乘除。亦不足言也。先生书学钟太傅。世称稷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09L 页
 下体。因其所居而名也。然方其在时。不甚贵也。今则一辞推重。待以师范。昔之矜才斗巧。自以为名世者。今皆懑然服矣。亦可见正道之终胜也。然不有 圣主之导率。岂其一变之至此。书法尚然。况文耶。重为世道幸也。遂为之备书。
下体。因其所居而名也。然方其在时。不甚贵也。今则一辞推重。待以师范。昔之矜才斗巧。自以为名世者。今皆懑然服矣。亦可见正道之终胜也。然不有 圣主之导率。岂其一变之至此。书法尚然。况文耶。重为世道幸也。遂为之备书。书安顺庵(鼎福)斥邪文后
顺庵安公于吾先子。未有倾盖之素。始于广津舟中。一面而相识也。造次之交。深于久要。盖相有目击而存者也。继此不再遇而不能相忘。公既屡道于人。而吾先子亦然。梅谷李公世杭,叶西权尚书𧟓。并吾乡之望而知公者也。故先子与之道此。而大中幸与闻焉。呜呼。此古君子之相知也。今世可复闻耶。公没而其著述始行于世。文献藉公而重。登于 乙览者多。而乃其斥邪之书。为其姻亲之陷于邪者作也。故辞繁意竭。如救焚溺而卒莫之救也。甚矣邪说之惑人也。终乃国禁加之。抵法者众。而公之姻亲及焉。公之言果验矣。然滋蔓犹未除也。今为举国之忧。于是世皆称公之先见。而想慕其风猷。况知公者耶。惜乎。李公亦没矣。是书来自权公。二公并亦早忧此也。大中虽未及觌公。而先谊讵敢忘哉。玆因权公之托。谨书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0H 页
 其卷后。而先之以广津之遇。若其斥邪之严。忧世之切。览是书者自知之。讵待于余言哉。
其卷后。而先之以广津之遇。若其斥邪之严。忧世之切。览是书者自知之。讵待于余言哉。书金先达(时和)诗轴后
玄川元公子才。返自海槎。卜居南巷。教授生徒。户屦常满。余亦屡至其室。藉草临泉。田园之娱足矣。然公犹以为不深。尽室入砥平之勿川。原骊之望。待以为重。梁氏凤凰台溪山绝胜。距公家十里。良辰暇日。公辄骑牛就之。梁氏老少。倾邻欣迓。鸡黍信宿。久而不懈。扁舟时至京洛。所过江墅。皆若行窝待之。平生未尝屈志求容。故常窝李公敏辅曰。子才利不能诱。威不能怵。柯汀赵公镇宽曰。勿老古之遗直。其见重于贤宰相如此。公常慕荀陈之淑乡。而教人各以其才。金君时和其一也。少尝以文发解。足以鸣世。而旋乃投笔举武科。盖其世业也。然意常在笔砚。有时赋诗联轴。犹是南郭之旧声也。对之如见玄川。为题其轴末。以识存没之感。且惜君之失路。然君子报国。文武何殊。君第致力其当分。期不负所受而已。岂以得失婴怀哉。
书深隐李公遗事后
英陵制作之治。黄,许两相为之佐。明良喜起。莫盛于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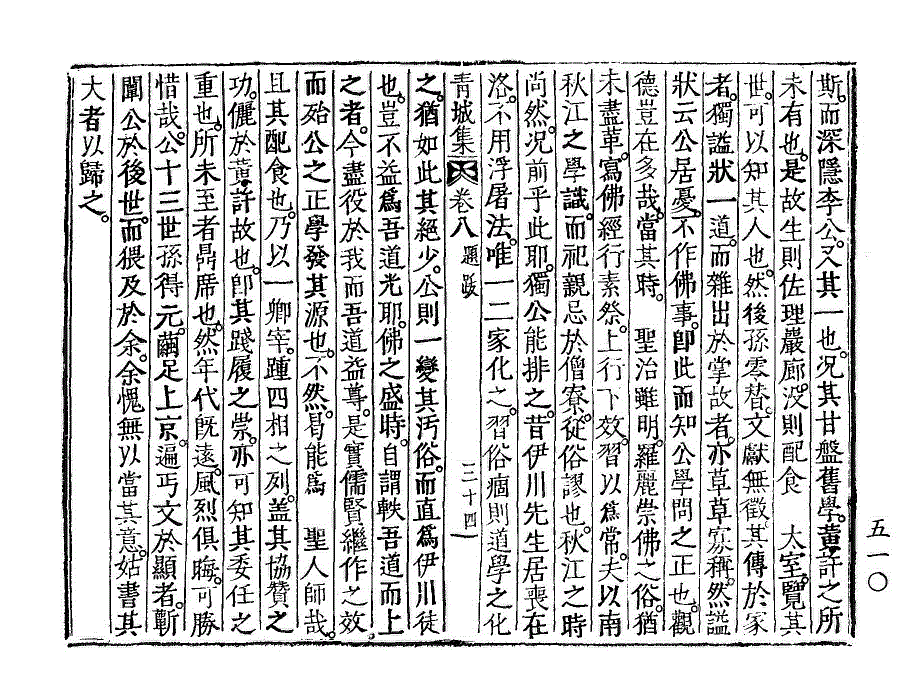 斯。而深隐李公。又其一也。况其甘盘旧学。黄,许之所未有也。是故生则佐理岩廊。没则配食 太室。览其世。可以知其人也。然后孙零替。文献无徵。其传于家者。独谥状一道。而杂出于掌故者。亦草草寡称。然谥状云公居忧。不作佛事。即此而知公学问之正也。观德岂在多哉。当其时。 圣治虽明。罗丽崇佛之俗。犹未尽革。写佛经行素祭。上行下效。习以为常。夫以南秋江之学识。而祀亲忌于僧寮。从俗谬也。秋江之时尚然。况前乎此耶。独公能排之。昔伊川先生居丧在洛。不用浮屠法。唯一二家化之。习俗痼则道学之化之。犹如此其绝少。公则一变其污俗。而直为伊川徒也。岂不益为吾道光耶。佛之盛时。自谓轶吾道而上之者。今尽役于我而吾道益尊。是实儒贤继作之效。而殆公之正学发其源也。不然。曷能为 圣人师哉。且其配食也。乃以一卿宰。踵四相之列。盖其协赞之功。俪于黄,许故也。即其践履之崇。亦可知其委任之重也。所未至者鼎席也。然年代既远。风烈俱晦。可胜惜哉。公十三世孙得元。茧足上京。遍丐文于显者。蕲阐公于后世。而猥及于余。余愧无以当其意。姑书其大者以归之。
斯。而深隐李公。又其一也。况其甘盘旧学。黄,许之所未有也。是故生则佐理岩廊。没则配食 太室。览其世。可以知其人也。然后孙零替。文献无徵。其传于家者。独谥状一道。而杂出于掌故者。亦草草寡称。然谥状云公居忧。不作佛事。即此而知公学问之正也。观德岂在多哉。当其时。 圣治虽明。罗丽崇佛之俗。犹未尽革。写佛经行素祭。上行下效。习以为常。夫以南秋江之学识。而祀亲忌于僧寮。从俗谬也。秋江之时尚然。况前乎此耶。独公能排之。昔伊川先生居丧在洛。不用浮屠法。唯一二家化之。习俗痼则道学之化之。犹如此其绝少。公则一变其污俗。而直为伊川徒也。岂不益为吾道光耶。佛之盛时。自谓轶吾道而上之者。今尽役于我而吾道益尊。是实儒贤继作之效。而殆公之正学发其源也。不然。曷能为 圣人师哉。且其配食也。乃以一卿宰。踵四相之列。盖其协赞之功。俪于黄,许故也。即其践履之崇。亦可知其委任之重也。所未至者鼎席也。然年代既远。风烈俱晦。可胜惜哉。公十三世孙得元。茧足上京。遍丐文于显者。蕲阐公于后世。而猥及于余。余愧无以当其意。姑书其大者以归之。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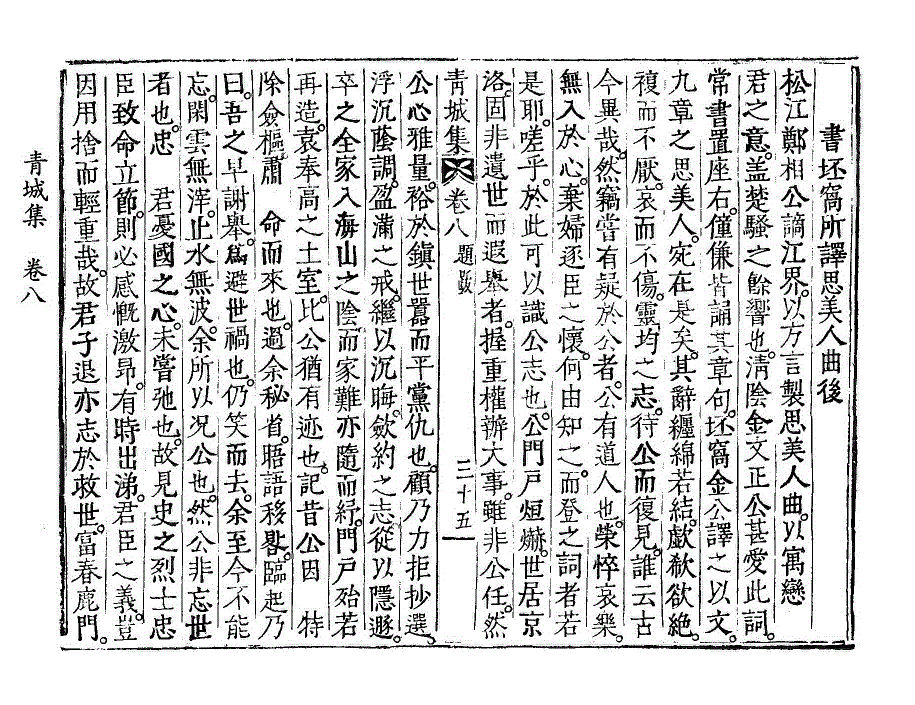 书坯窝所译思美人曲后
书坯窝所译思美人曲后松江郑相公谪江界。以方言制思美人曲。以寓恋 君之意。盖楚骚之馀响也。清阴金文正公甚爱此词。常书置座右。僮傔皆诵其章句。坯窝金公译之以文。九章之思美人。宛在是矣。其辞缠绵若结。歔欷欲绝。复而不厌。哀而不伤。灵均之志。待公而复见。谁云古今异哉。然窃尝有疑于公者。公有道人也。荣悴哀乐。无入于心。弃妇逐臣之怀。何由知之。而登之词者若是耶。嗟乎。于此可以识公志也。公门户烜赫。世居京洛。固非遗世而遐举者。握重权办大事。虽非公任。然公心雅量。裕于镇世嚣而平党仇也。顾乃力拒抄选。浮沉荫调。盈满之戒。继以沉晦。敛约之志。从以隐遁。卒之全家入海山之阴。而家难亦随而纾。门户殆若再造。袁奉高之土室。比公犹有迹也。记昔公因 特除佥枢。肃 命而来也。过余秘省。晤语移晷。临起乃曰。吾之早谢举。为避世祸也。仍笑而去。余至今不能忘。闲云无滓。止水无波。余所以况公也。然公非忘世者也。忠 君忧国之心。未尝弛也。故见史之烈士忠臣致命立节。则必感慨激昂。有时出涕。君臣之义。岂因用舍而轻重哉。故君子退亦志于救世。富春鹿门。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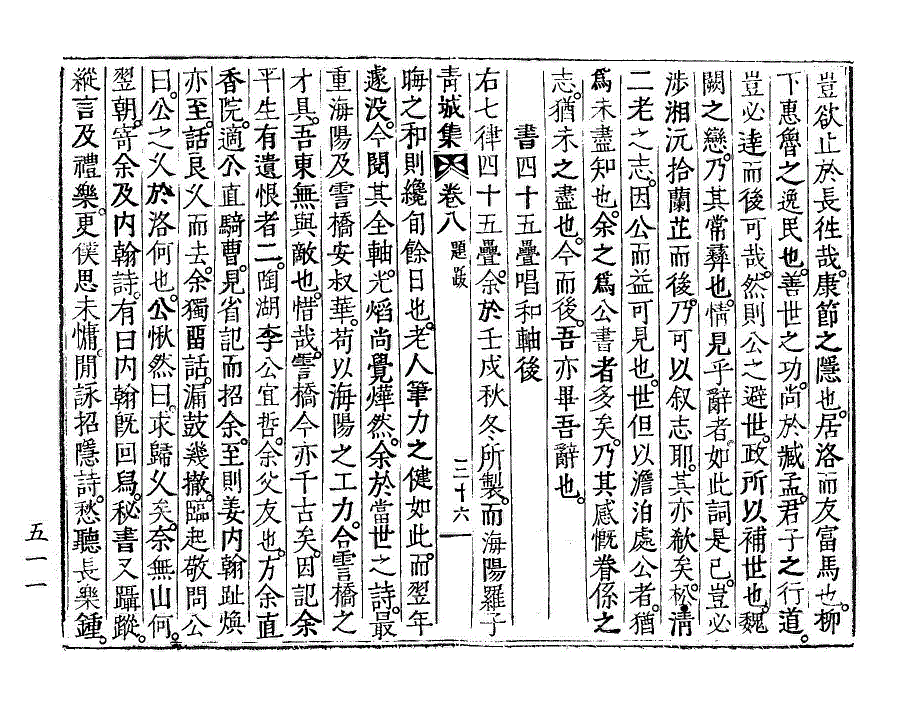 岂欲止于长往哉。康节之隐也。居洛而友富马也。柳下惠鲁之逸民也。善世之功。尚于臧孟。君子之行道。岂必达而后可哉。然则公之避世。政所以补世也。魏阙之恋。乃其常彝也。情见乎辞者。如此词是已。岂必涉湘沅拾兰芷而后。乃可以叙志耶。其亦欷矣。松,清二老之志。因公而益可见也。世但以澹泊处公者。犹为未尽知也。余之为公书者多矣。乃其感慨眷系之志。犹未之尽也。今而后。吾亦毕吾辞也。
岂欲止于长往哉。康节之隐也。居洛而友富马也。柳下惠鲁之逸民也。善世之功。尚于臧孟。君子之行道。岂必达而后可哉。然则公之避世。政所以补世也。魏阙之恋。乃其常彝也。情见乎辞者。如此词是已。岂必涉湘沅拾兰芷而后。乃可以叙志耶。其亦欷矣。松,清二老之志。因公而益可见也。世但以澹泊处公者。犹为未尽知也。余之为公书者多矣。乃其感慨眷系之志。犹未之尽也。今而后。吾亦毕吾辞也。书四十五叠唱和轴后
右七律四十五叠。余于壬戌秋冬所制。而海阳罗子晦之和则才旬馀日也。老人笔力之健如此。而翌年遽没。今阅其全轴。光焰尚觉烨然。余于当世之诗。最重海阳及霅桥安叔华。苟以海阳之工力。合霅桥之才具。吾东无与敌也。惜哉。霅桥今亦千古矣。因记余平生有遗恨者二。陶湖李公宜哲。余父友也。方余直香院。适公直骑曹。见省记而招余。至则姜内翰趾焕亦至。话良久而去。余独留话。漏鼓几撤。临起敬问公曰。公之久于洛何也。公愀然曰。求归久矣。奈无山何。翌朝。寄余及内翰诗。有曰内翰既回舄。秘书又蹑踪。纵言及礼乐。更仆思未慵。閒咏招隐诗。愁听长乐钟。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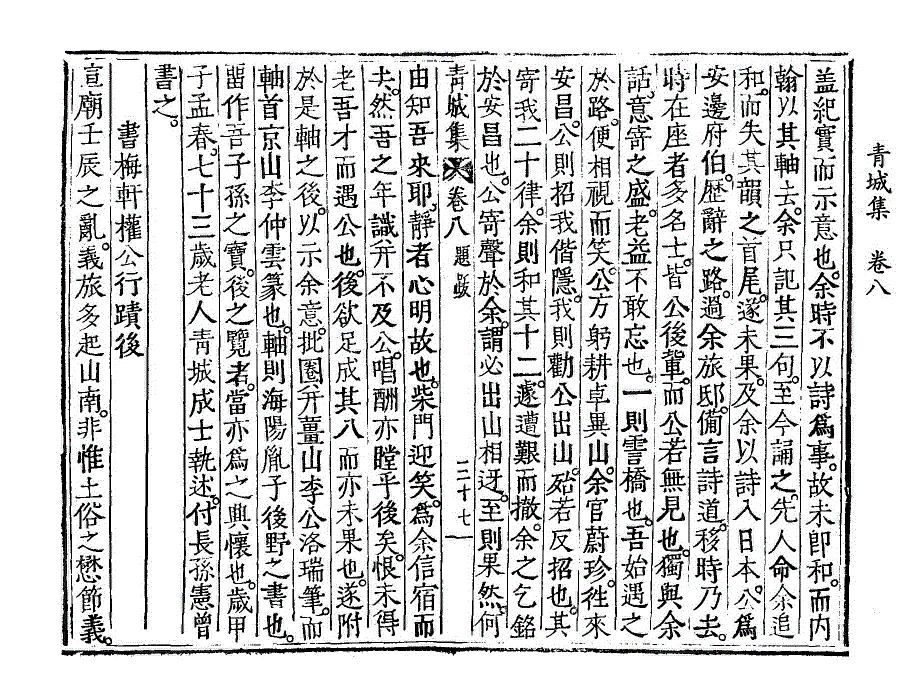 盖纪实而示意也。余时不以诗为事。故未即和。而内翰以其轴去。余只记其三句。至今诵之。先人命余追和。而失其韵之首尾。遂未果。及余以诗入日本。公为安边府伯。历辞之路。过余旅邸。备言诗道。移时乃去。时在座者多名士。皆公后辈。而公若无见也。独与余话。意寄之盛。老益不敢忘也。一则霅桥也。吾始遇之于路。便相视而笑。公方躬耕卓异山。余官蔚珍。往来安昌。公则招我偕隐。我则劝公出山。殆若反招也。其寄我二十律。余则和其十二。遽遭艰而撤。余之乞铭于安昌也。公寄声于余。谓必出山相迓。至则果然。何由知吾来耶。静者心明故也。柴门迎笑。为余信宿而去。然吾之年识并不及公。唱酬亦瞠乎后矣。恨未得老吾才而遇公也。后欲足成其八而亦未果也。遂附于是轴之后。以示余意。批圈并姜山李公洛瑞笔。而轴首京山李仲云篆也。轴则海阳胤子后野之书也。留作吾子孙之宝。后之览者。当亦为之兴怀也。岁甲子孟春。七十三岁老人青城成士执述。付长孙宪曾书之。
盖纪实而示意也。余时不以诗为事。故未即和。而内翰以其轴去。余只记其三句。至今诵之。先人命余追和。而失其韵之首尾。遂未果。及余以诗入日本。公为安边府伯。历辞之路。过余旅邸。备言诗道。移时乃去。时在座者多名士。皆公后辈。而公若无见也。独与余话。意寄之盛。老益不敢忘也。一则霅桥也。吾始遇之于路。便相视而笑。公方躬耕卓异山。余官蔚珍。往来安昌。公则招我偕隐。我则劝公出山。殆若反招也。其寄我二十律。余则和其十二。遽遭艰而撤。余之乞铭于安昌也。公寄声于余。谓必出山相迓。至则果然。何由知吾来耶。静者心明故也。柴门迎笑。为余信宿而去。然吾之年识并不及公。唱酬亦瞠乎后矣。恨未得老吾才而遇公也。后欲足成其八而亦未果也。遂附于是轴之后。以示余意。批圈并姜山李公洛瑞笔。而轴首京山李仲云篆也。轴则海阳胤子后野之书也。留作吾子孙之宝。后之览者。当亦为之兴怀也。岁甲子孟春。七十三岁老人青城成士执述。付长孙宪曾书之。书梅轩权公行迹后
宣庙壬辰之乱。义旅多起山南。非惟土俗之懋节义。
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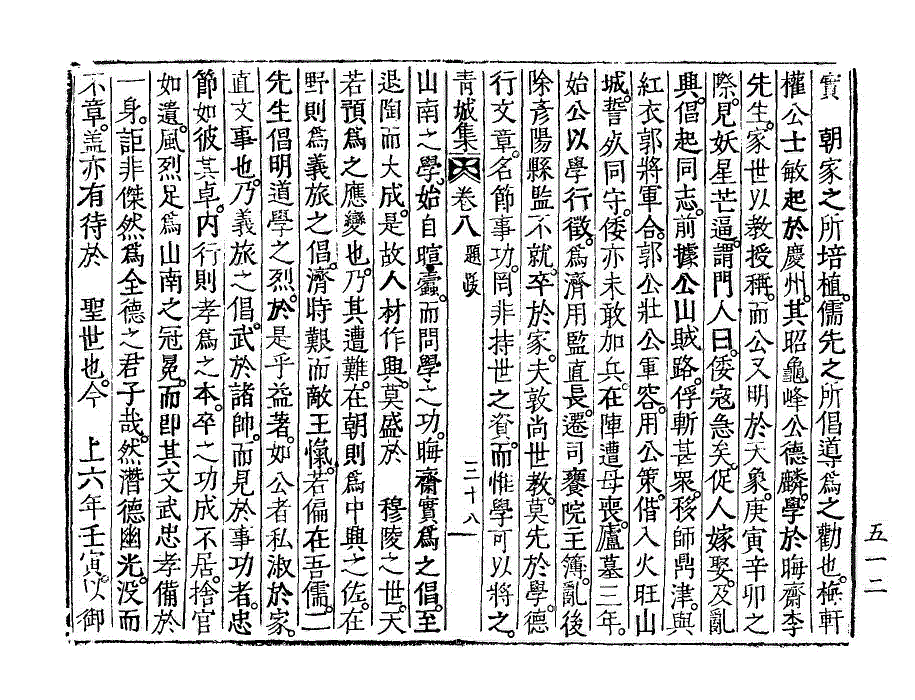 实 朝家之所培植。儒先之所倡导为之劝也。梅轩权公士敏起于庆州。其昭龟峰公德麟。学于晦斋李先生。家世以教授称。而公又明于天象。庚寅辛卯之际。见妖星芒逼。谓门人曰。倭寇急矣。促人嫁娶。及乱兴。倡起同志。前据公山贼路。俘斩甚众。移师鼎津。与红衣郭将军合。郭公壮公军容。用公策。偕入火旺山城。誓死同守。倭亦未敢加兵。在阵遭母丧。庐墓三年。始公以学行徵。为济用监直长。迁司饔院主簿。乱后除彦阳县监不就。卒于家。夫敦尚世教。莫先于学。德行文章。名节事功。罔非持世之资。而惟学可以将之。山南之学。始自暄,蠹。而问学之功。晦斋实为之倡。至退陶而大成。是故人材作兴。莫盛于 穆陵之世。天若预为之应变也。乃其遭难。在朝则为中兴之佐。在野则为义旅之倡。济时艰而敌王忾。若偏在吾儒。二先生倡明道学之烈。于是乎益著。如公者私淑于家。直文事也。乃义旅之倡。武于诸帅。而见于事功者。忠节如彼其卓。内行则孝为之本。卒之功成不居。舍官如遗。风烈足为山南之冠冕。而即其文武忠孝备于一身。讵非杰然为全德之君子哉。然潜德幽光。没而不章。盖亦有待于 圣世也。今 上六年壬寅。以御
实 朝家之所培植。儒先之所倡导为之劝也。梅轩权公士敏起于庆州。其昭龟峰公德麟。学于晦斋李先生。家世以教授称。而公又明于天象。庚寅辛卯之际。见妖星芒逼。谓门人曰。倭寇急矣。促人嫁娶。及乱兴。倡起同志。前据公山贼路。俘斩甚众。移师鼎津。与红衣郭将军合。郭公壮公军容。用公策。偕入火旺山城。誓死同守。倭亦未敢加兵。在阵遭母丧。庐墓三年。始公以学行徵。为济用监直长。迁司饔院主簿。乱后除彦阳县监不就。卒于家。夫敦尚世教。莫先于学。德行文章。名节事功。罔非持世之资。而惟学可以将之。山南之学。始自暄,蠹。而问学之功。晦斋实为之倡。至退陶而大成。是故人材作兴。莫盛于 穆陵之世。天若预为之应变也。乃其遭难。在朝则为中兴之佐。在野则为义旅之倡。济时艰而敌王忾。若偏在吾儒。二先生倡明道学之烈。于是乎益著。如公者私淑于家。直文事也。乃义旅之倡。武于诸帅。而见于事功者。忠节如彼其卓。内行则孝为之本。卒之功成不居。舍官如遗。风烈足为山南之冠冕。而即其文武忠孝备于一身。讵非杰然为全德之君子哉。然潜德幽光。没而不章。盖亦有待于 圣世也。今 上六年壬寅。以御青城集卷之八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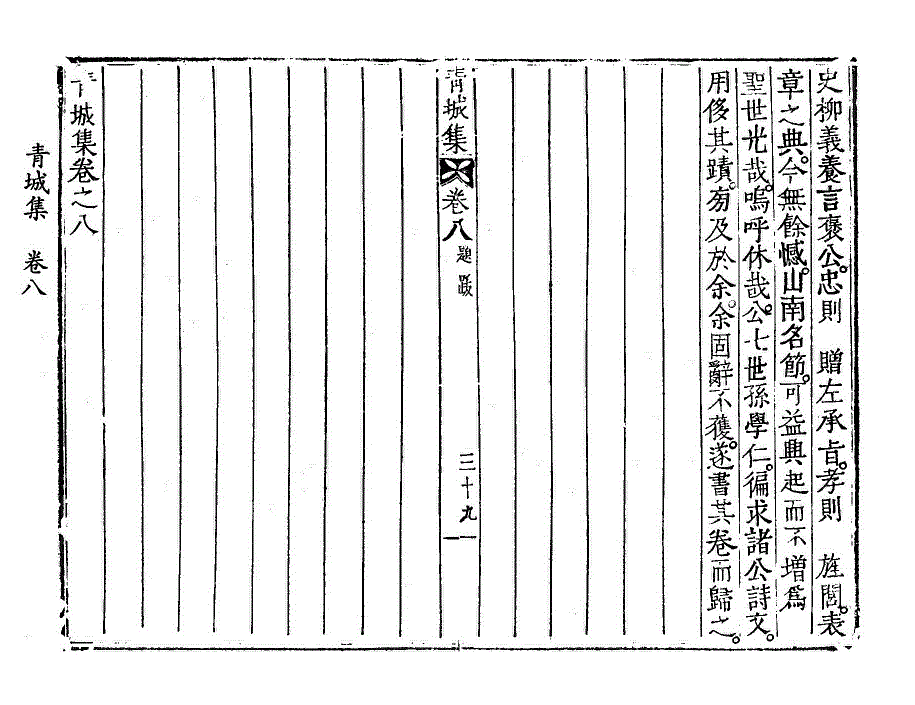 史柳义养言褒公。忠则 赠左承旨。孝则 旌闾。表章之典。今无馀憾。山南名节。可益兴起而不增为 圣世光哉。呜呼休哉。公七世孙学仁。遍求诸公诗文。用侈其迹。旁及于余。余固辞不获。遂书其卷而归之。
史柳义养言褒公。忠则 赠左承旨。孝则 旌闾。表章之典。今无馀憾。山南名节。可益兴起而不增为 圣世光哉。呜呼休哉。公七世孙学仁。遍求诸公诗文。用侈其迹。旁及于余。余固辞不获。遂书其卷而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