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荷栖集卷之七 第 x 页
荷栖集卷之七
记
记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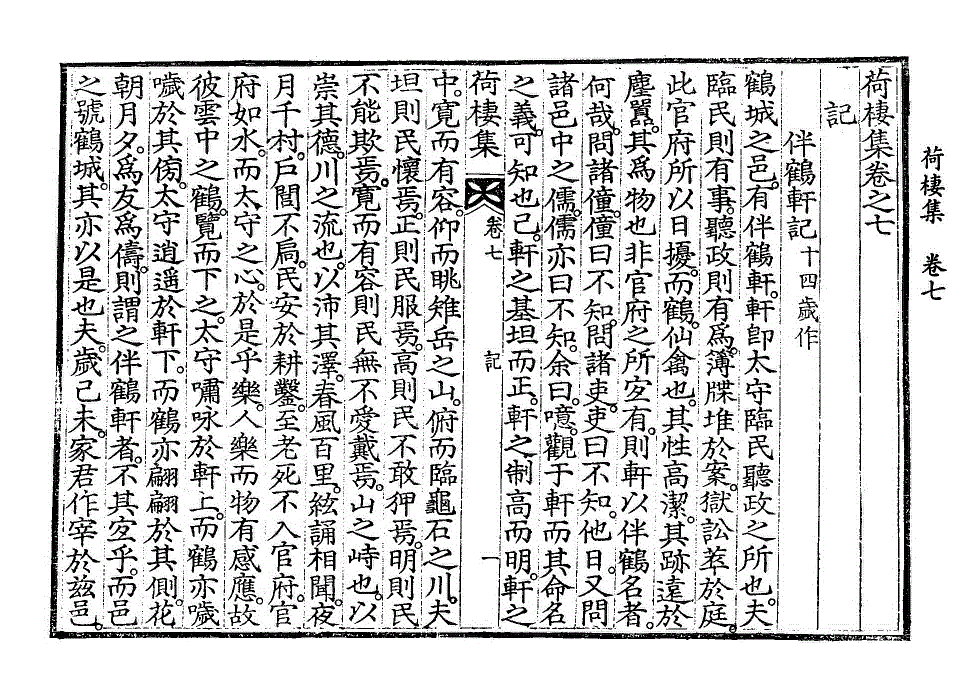 伴鹤轩记(十四岁作)
伴鹤轩记(十四岁作)鹤城之邑。有伴鹤轩。轩即太守临民听政之所也。夫临民则有事。听政则有为。簿牒堆于案。狱讼萃于庭。此官府所以日扰。而鹤。仙禽也。其性高洁。其迹远于尘嚣。其为物也非官府之所宜有。则轩以伴鹤名者。何哉。问诸僮。僮曰不知。问诸吏。吏曰不知。他日。又问诸邑中之儒。儒亦曰不知。余曰。噫。观于轩而其命名之义。可知也已。轩之基坦而正。轩之制高而明。轩之中。宽而有容。仰而眺雉岳之山。俯而临龟石之川。夫坦则民怀焉。正则民服焉。高则民不敢狎焉。明则民不能欺焉。宽而有容则民无不爱戴焉。山之峙也。以崇其德。川之流也。以沛其泽。春风百里。弦诵相闻。夜月千村。户闾不扃。民安于耕凿。至老死不入官府。官府如水。而太守之心。于是乎乐。人乐而物有感应。故彼云中之鹤。览而下之。太守啸咏于轩上。而鹤亦哕哕于其傍。太守逍遥于轩下。而鹤亦翩翩于其侧。花朝月夕。为友为俦。则谓之伴鹤轩者。不其宜乎。而邑之号鹤城。其亦以是也夫。岁己未。家君作宰于玆邑。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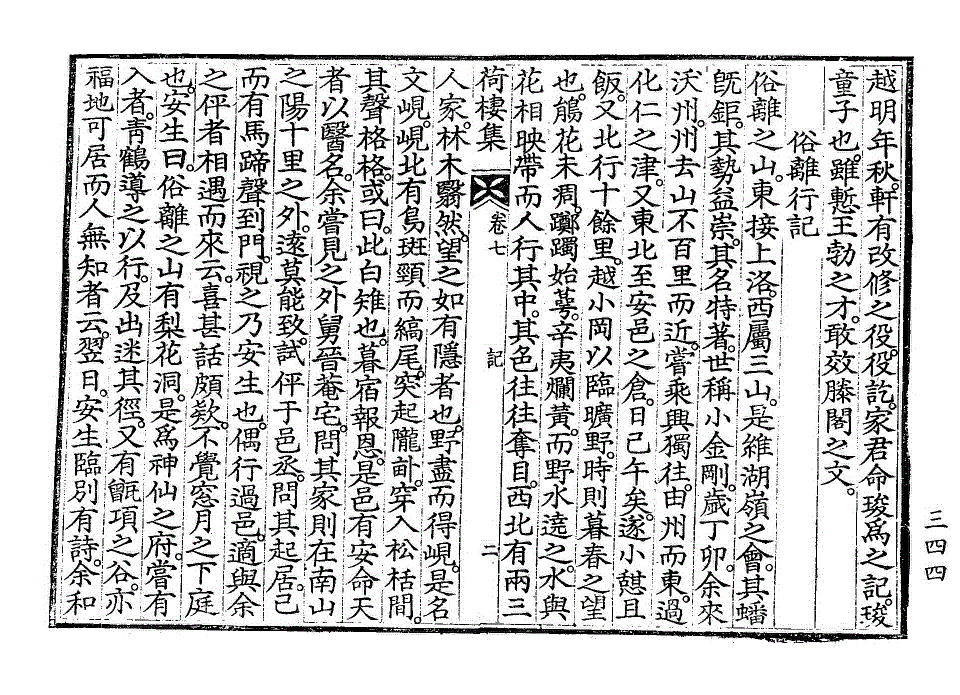 越明年秋。轩有改修之役。役讫。家君命㻐为之记。㻐童子也。虽惭王勃之才。敢效滕阁之文。
越明年秋。轩有改修之役。役讫。家君命㻐为之记。㻐童子也。虽惭王勃之才。敢效滕阁之文。俗离行记
俗离之山。东接上洛。西属三山。是维湖岭之会。其蟠既钜。其势益崇。其名特著。世称小金刚。岁丁卯。余来沃州。州去山不百里而近。尝乘兴独往。由州而东。过化仁之津。又东北至安邑之仓。日已午矣。遂小憩且饭。又北行十馀里。越小冈以临旷野。时则暮春之望也。鹃花未凋。踯躅始萼。辛夷烂黄。而野水绕之。水与花相映带而人行其中。其色往往夺目。西北有两三人家。林木翳然。望之如有隐者也。野尽而得岘。是名文岘。岘北有鸟斑颈而缟尾。突起陇亩。穿入松栝间。其声格格。或曰。此白雉也。暮宿报恩。是邑有安命天者以医名。余尝见之外舅晋庵宅。问其家则在南山之阳十里之外。远莫能致。试伻于邑丞。问其起居。已而有马蹄声到门。视之乃安生也。偶行过邑。适与余之伻者相遇而来云。喜甚话颇款。不觉窗月之下庭也。安生曰。俗离之山有梨花洞。是为神仙之府。尝有入者。青鹤导之以行。及出迷其径。又有甑项之谷。亦福地可居而人无知者云。翌日。安生临别有诗。余和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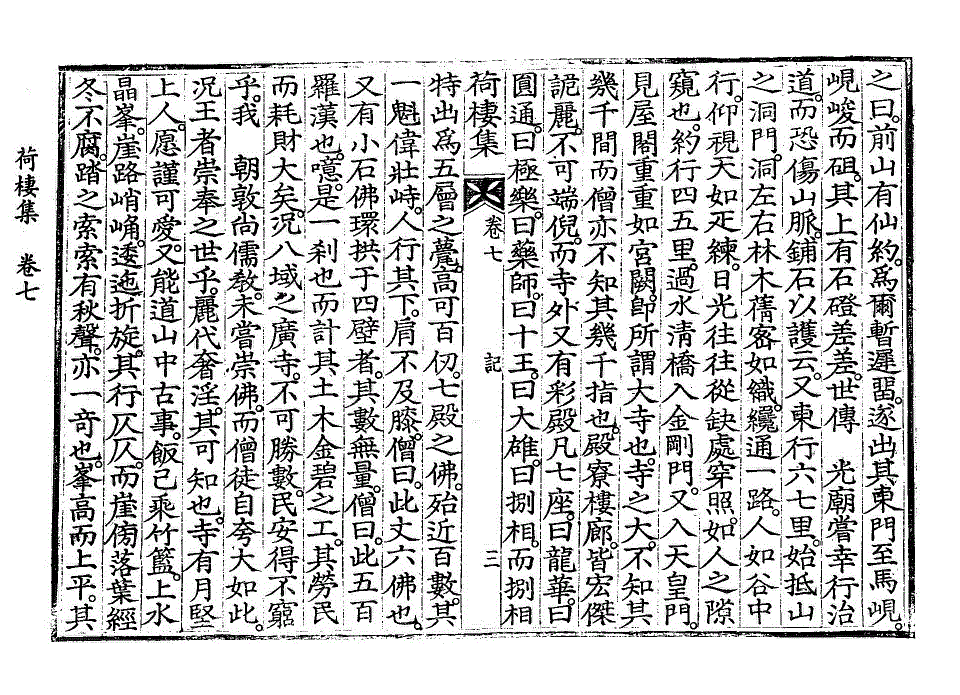 之曰。前山有仙约。为尔暂迟留。遂出其东门至马岘。岘峻而砠。其上有石磴差差。世传 光庙尝幸行治道。而恐伤山脉。铺石以护云。又东行六七里。始抵山之洞门。洞左右林木茜密如织。才通一路。人如谷中行。仰视天如疋练。日光往往从缺处穿照。如人之隙窥也。约行四五里。过水清桥入金刚门。又入天皇门。见屋阁重重如宫阙。即所谓大寺也。寺之大。不知其几千间而僧亦不知其几千指也。殿寮楼廊。皆宏杰诡丽。不可端倪。而寺外又有彩殿凡七座。曰龙华。曰圆通。曰极乐。曰药师。曰十王。曰大雄。曰捌相。而捌相特出为五层之甍。高可百仞。七殿之佛。殆近百数。其一魁伟壮峙。人行其下。肩不及膝。僧曰。此丈六佛也。又有小石佛环拱于四壁者。其数无量。僧曰。此五百罗汉也。噫。是一刹也而计其土木金碧之工。其劳民而耗财大矣。况八域之广寺。不可胜数。民安得不穷乎。我 朝敦尚儒教。未尝崇佛。而僧徒自夸大如此。况王者崇奉之世乎。丽代奢淫。其可知也。寺有月坚上人。愿谨可爱。又能道山中古事。饭已乘竹篮。上水晶峰。崖路峭崅。逶迤折旋。其行仄仄。而崖傍落叶经冬不腐。踏之索索有秋声。亦一奇也。峰高而上平。其
之曰。前山有仙约。为尔暂迟留。遂出其东门至马岘。岘峻而砠。其上有石磴差差。世传 光庙尝幸行治道。而恐伤山脉。铺石以护云。又东行六七里。始抵山之洞门。洞左右林木茜密如织。才通一路。人如谷中行。仰视天如疋练。日光往往从缺处穿照。如人之隙窥也。约行四五里。过水清桥入金刚门。又入天皇门。见屋阁重重如宫阙。即所谓大寺也。寺之大。不知其几千间而僧亦不知其几千指也。殿寮楼廊。皆宏杰诡丽。不可端倪。而寺外又有彩殿凡七座。曰龙华。曰圆通。曰极乐。曰药师。曰十王。曰大雄。曰捌相。而捌相特出为五层之甍。高可百仞。七殿之佛。殆近百数。其一魁伟壮峙。人行其下。肩不及膝。僧曰。此丈六佛也。又有小石佛环拱于四壁者。其数无量。僧曰。此五百罗汉也。噫。是一刹也而计其土木金碧之工。其劳民而耗财大矣。况八域之广寺。不可胜数。民安得不穷乎。我 朝敦尚儒教。未尝崇佛。而僧徒自夸大如此。况王者崇奉之世乎。丽代奢淫。其可知也。寺有月坚上人。愿谨可爱。又能道山中古事。饭已乘竹篮。上水晶峰。崖路峭崅。逶迤折旋。其行仄仄。而崖傍落叶经冬不腐。踏之索索有秋声。亦一奇也。峰高而上平。其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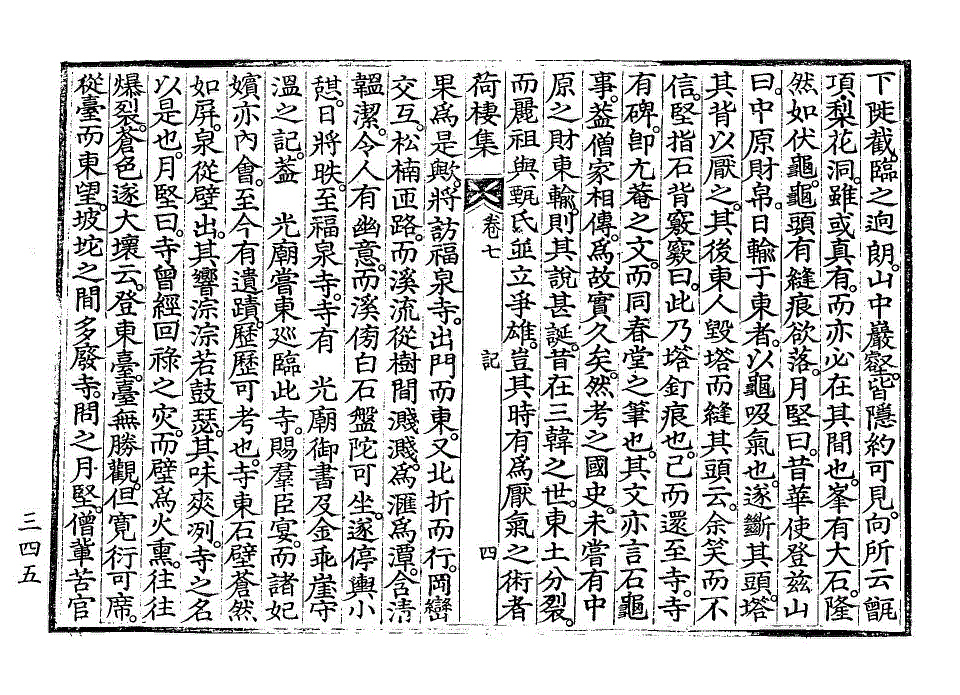 下陡截。临之迥朗。山中岩壑。皆隐约可见。向所云甑项,梨花洞。虽或真有。而亦必在其间也。峰有大石。隆然如伏龟。龟头有缝痕欲落。月坚曰。昔华使登玆山曰。中原财帛。日输于东者。以龟吸气也。遂断其头。塔其背以厌之。其后东人毁塔而缝其头云。余笑而不信。坚指石背窍窾曰。此乃塔钉痕也。已而还至寺。寺有碑。即尤庵之文。而同春堂之笔也。其文亦言石龟事。盖僧家相传。为故实久矣。然考之国史。未尝有中原之财东输。则其说甚诞。昔在三韩之世。东土分裂。而丽祖与甄氏并立争雄。岂其时有为厌气之术者果为是欤。将访福泉寺。出门而东。又北折而行。冈峦交互。松楠匝路。而溪流从树间溅溅。为𣿬为潭。含清韫洁。令人有幽意。而溪傍白石盘陀可坐。遂停舆小憩。日将昳。至福泉寺。寺有 光庙御书及金乖崖守温之记。盖 光庙尝东巡临此寺。赐群臣宴。而诸妃嫔亦内会。至今有遗迹。历历可考也。寺东石壁苍然如屏。泉从壁出。其响淙淙若鼓瑟。其味爽冽。寺之名以是也。月坚曰。寺曾经回禄之灾。而壁为火熏。往往爆裂。苍色遂大坏云。登东台。台无胜观。但宽衍可席。从台而东望。坡坨之间多废寺。问之月坚。僧辈苦官
下陡截。临之迥朗。山中岩壑。皆隐约可见。向所云甑项,梨花洞。虽或真有。而亦必在其间也。峰有大石。隆然如伏龟。龟头有缝痕欲落。月坚曰。昔华使登玆山曰。中原财帛。日输于东者。以龟吸气也。遂断其头。塔其背以厌之。其后东人毁塔而缝其头云。余笑而不信。坚指石背窍窾曰。此乃塔钉痕也。已而还至寺。寺有碑。即尤庵之文。而同春堂之笔也。其文亦言石龟事。盖僧家相传。为故实久矣。然考之国史。未尝有中原之财东输。则其说甚诞。昔在三韩之世。东土分裂。而丽祖与甄氏并立争雄。岂其时有为厌气之术者果为是欤。将访福泉寺。出门而东。又北折而行。冈峦交互。松楠匝路。而溪流从树间溅溅。为𣿬为潭。含清韫洁。令人有幽意。而溪傍白石盘陀可坐。遂停舆小憩。日将昳。至福泉寺。寺有 光庙御书及金乖崖守温之记。盖 光庙尝东巡临此寺。赐群臣宴。而诸妃嫔亦内会。至今有遗迹。历历可考也。寺东石壁苍然如屏。泉从壁出。其响淙淙若鼓瑟。其味爽冽。寺之名以是也。月坚曰。寺曾经回禄之灾。而壁为火熏。往往爆裂。苍色遂大坏云。登东台。台无胜观。但宽衍可席。从台而东望。坡坨之间多废寺。问之月坚。僧辈苦官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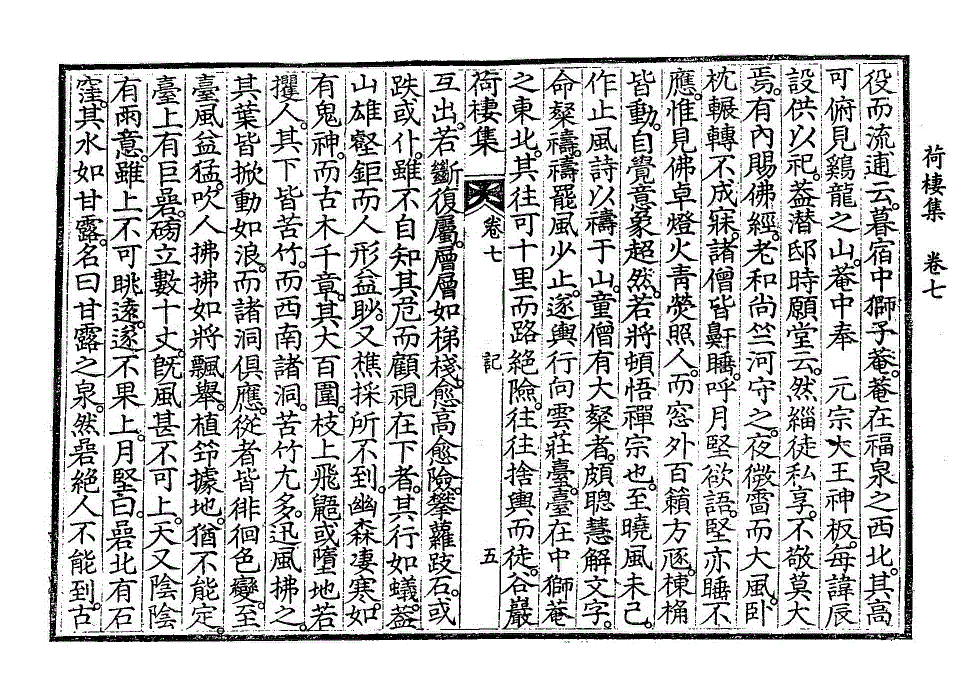 役而流逋云。暮宿中狮子庵。庵在福泉之西北。其高可俯见鸡龙之山。庵中奉 元宗大王神板。每讳辰设供以祀。盖潜邸时愿堂云。然缁徒私享。不敬莫大焉。有内赐佛经。老和尚竺河守之。夜微䨓而大风。卧枕辗转不成寐。诸僧皆鼾睡。呼月坚欲语。坚亦睡不应。惟见佛卓灯火青荧照人。而窗外百籁方豗。栋桷皆动。自觉意象超然。若将顿悟禅宗也。至晓风未已。作止风诗以祷于山。童僧有大粲者。颇聪慧解文字。命粲祷。祷罢风少止。遂舆行向云庄台。台在中狮庵之东北。其往可十里而路绝险。往往舍舆而徒。谷岩互出。若断复属。层层如梯栈。愈高愈险。攀萝跂石。或跌或仆。虽不自知其危而顾视在下者。其行如蚁。盖山雄壑钜而人形益眇。又樵采所不到。幽森凄寒。如有鬼神。而古木千章。其大百围。枝上飞鼯或堕地若攫人。其下皆苦竹。而西南诸洞。苦竹尤多。迅风拂之。其叶皆掀动如浪。而诸洞俱应。从者皆徘徊色变。至台风益猛。吹人拂拂如将飘举。植筇据地。犹不能定。台上有巨碞。磅立数十丈。既风甚不可上。天又阴阴有雨意。虽上不可眺远。遂不果上。月坚曰。碞北有石洼。其水如甘露。名曰甘露之泉。然碞绝人不能到。古
役而流逋云。暮宿中狮子庵。庵在福泉之西北。其高可俯见鸡龙之山。庵中奉 元宗大王神板。每讳辰设供以祀。盖潜邸时愿堂云。然缁徒私享。不敬莫大焉。有内赐佛经。老和尚竺河守之。夜微䨓而大风。卧枕辗转不成寐。诸僧皆鼾睡。呼月坚欲语。坚亦睡不应。惟见佛卓灯火青荧照人。而窗外百籁方豗。栋桷皆动。自觉意象超然。若将顿悟禅宗也。至晓风未已。作止风诗以祷于山。童僧有大粲者。颇聪慧解文字。命粲祷。祷罢风少止。遂舆行向云庄台。台在中狮庵之东北。其往可十里而路绝险。往往舍舆而徒。谷岩互出。若断复属。层层如梯栈。愈高愈险。攀萝跂石。或跌或仆。虽不自知其危而顾视在下者。其行如蚁。盖山雄壑钜而人形益眇。又樵采所不到。幽森凄寒。如有鬼神。而古木千章。其大百围。枝上飞鼯或堕地若攫人。其下皆苦竹。而西南诸洞。苦竹尤多。迅风拂之。其叶皆掀动如浪。而诸洞俱应。从者皆徘徊色变。至台风益猛。吹人拂拂如将飘举。植筇据地。犹不能定。台上有巨碞。磅立数十丈。既风甚不可上。天又阴阴有雨意。虽上不可眺远。遂不果上。月坚曰。碞北有石洼。其水如甘露。名曰甘露之泉。然碞绝人不能到。古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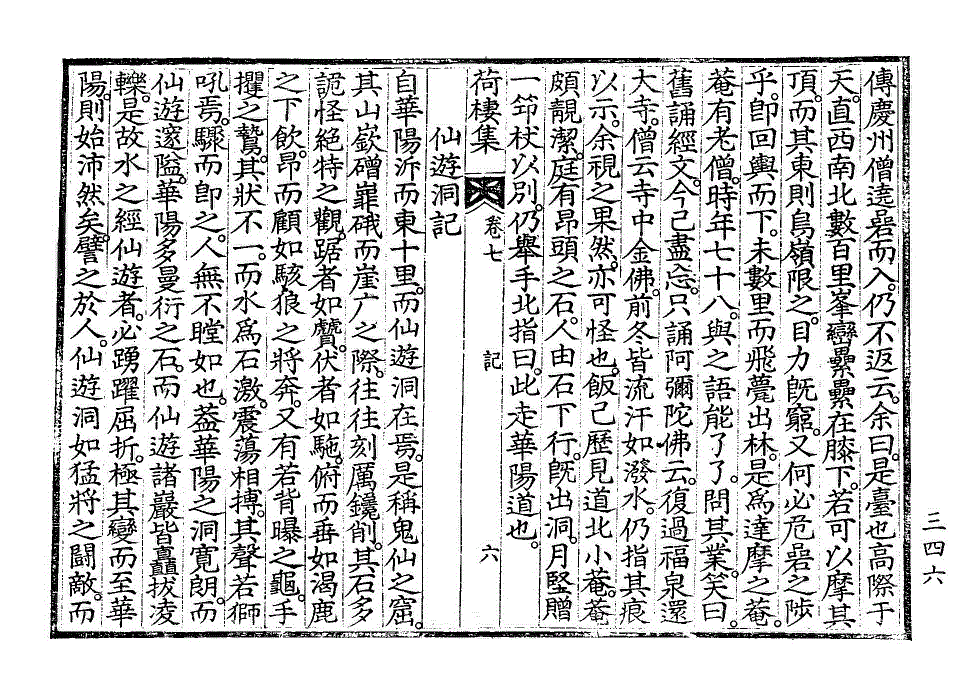 传庆州僧绕碞而入。仍不返云。余曰。是台也高际于天。直西南北数百里峰峦累累在膝下。若可以摩其顶。而其东则鸟岭限之。目力既穷。又何必危碞之陟乎。即回舆而下。未数里而飞甍出林。是为达摩之庵。庵有老僧。时年七十八。与之语能了了。问其业。笑曰。旧诵经文。今已尽忘。只诵阿弥陀佛云。复过福泉还大寺。僧云寺中金佛。前冬皆流汗如泼水。仍指其痕以示。余视之果然。亦可怪也。饭已历见道北小庵。庵颇靓洁。庭有昂头之石。人由石下行。既出洞。月坚赠一筇杖以别。仍举手北指曰。此走华阳道也。
传庆州僧绕碞而入。仍不返云。余曰。是台也高际于天。直西南北数百里峰峦累累在膝下。若可以摩其顶。而其东则鸟岭限之。目力既穷。又何必危碞之陟乎。即回舆而下。未数里而飞甍出林。是为达摩之庵。庵有老僧。时年七十八。与之语能了了。问其业。笑曰。旧诵经文。今已尽忘。只诵阿弥陀佛云。复过福泉还大寺。僧云寺中金佛。前冬皆流汗如泼水。仍指其痕以示。余视之果然。亦可怪也。饭已历见道北小庵。庵颇靓洁。庭有昂头之石。人由石下行。既出洞。月坚赠一筇杖以别。仍举手北指曰。此走华阳道也。仙游洞记
自华阳溯而东十里。而仙游洞在焉。是称鬼仙之窟。其山嵚磳㠑硪而崖广之际。往往刻厉镵削。其石多诡怪绝特之观。踞者如贙。伏者如驼。俯而垂如渴鹿之下饮。昂而顾如骇狼之将奔。又有若背曝之龟。手攫之鸷。其状不一。而水为石激。震荡相搏。其声若狮吼焉。骤而即之。人无不瞠如也。盖华阳之洞宽朗。而仙游邃隘。华阳多曼衍之石。而仙游诸岩皆矗拔凌轹。是故水之经仙游者。必踊跃屈折。极其变而至华阳。则始沛然矣。譬之于人。仙游洞如猛将之斗敌。而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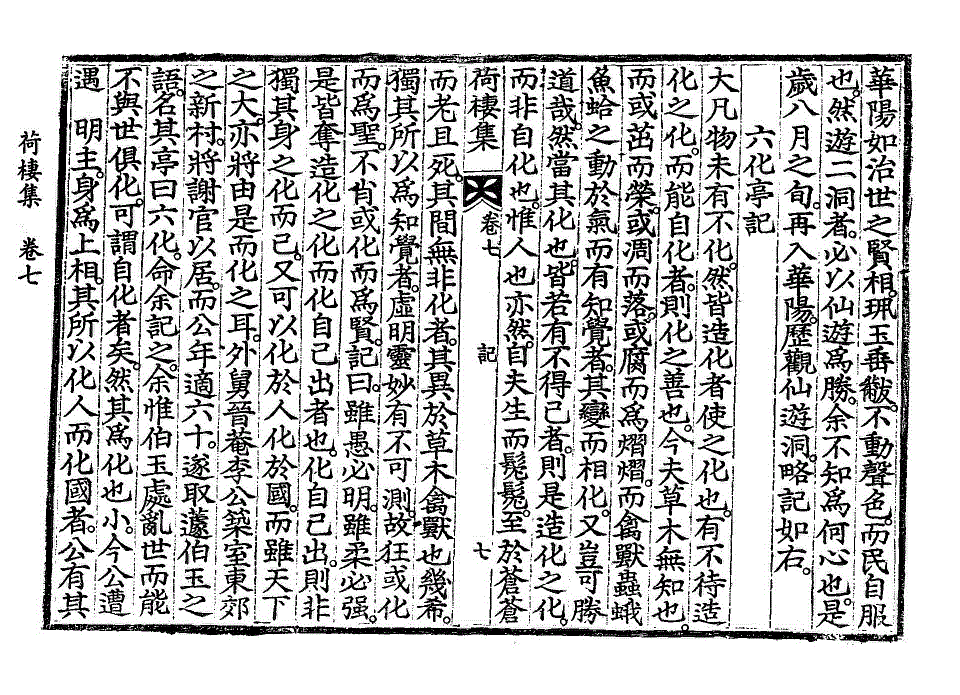 华阳如治世之贤相。佩玉垂黻。不动声色。而民自服也。然游二洞者。必以仙游为胜。余不知为何心也。是岁八月之旬。再入华阳。历观仙游洞。略记如右。
华阳如治世之贤相。佩玉垂黻。不动声色。而民自服也。然游二洞者。必以仙游为胜。余不知为何心也。是岁八月之旬。再入华阳。历观仙游洞。略记如右。六化亭记
大凡物未有不化。然皆造化者使之化也。有不待造化之化。而能自化者。则化之善也。今夫草木无知也。而或茁而荣。或凋而落。或腐而为熠熠。而禽兽虫蛾鱼蛤之动于气而有知觉者。其变而相化。又岂可胜道哉。然当其化也。皆若有不得已者。则是造化之化。而非自化也。惟人也亦然。自夫生而髧髧。至于苍苍而老且死。其间无非化者。其异于草木禽兽也几希。独其所以为知觉者。虚明灵妙有不可测。故狂或化而为圣。不肖或化而为贤。记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是皆夺造化之化而化自己出者也。化自己出。则非独其身之化而已。又可以化于人化于国。而虽天下之大。亦将由是而化之耳。外舅晋庵李公筑室东郊之新村。将谢官以居。而公年适六十。遂取蘧伯玉之语。名其亭曰六化。命余记之。余惟伯玉处乱世而能不与世俱化。可谓自化者矣。然其为化也小。今公遭遇 明主。身为上相。其所以化人而化国者。公有其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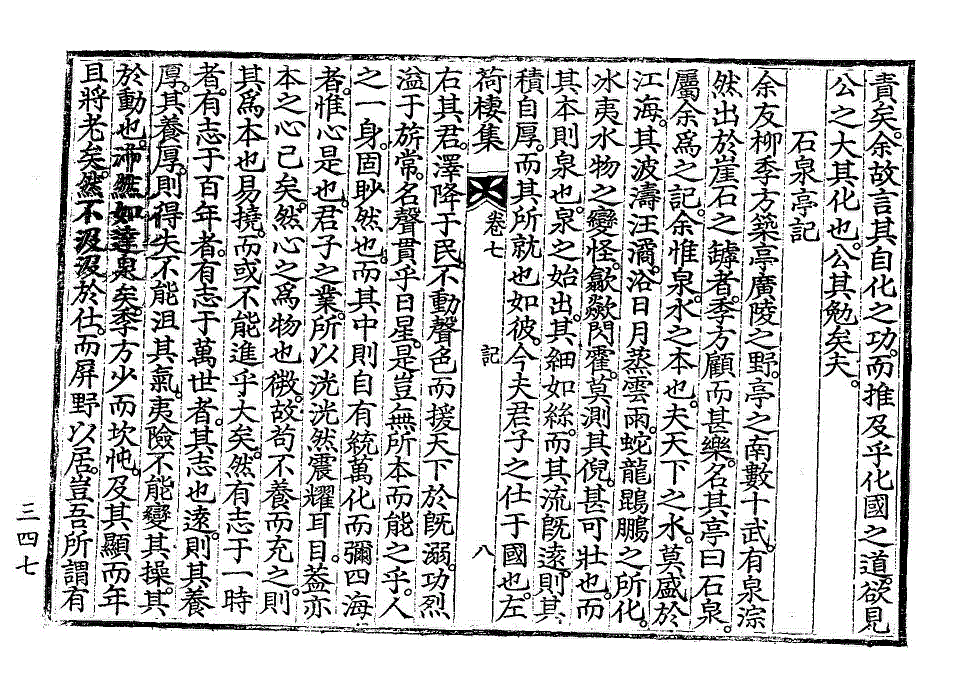 责矣。余故言其自化之功。而推及乎化国之道。欲见公之大其化也。公其勉矣夫。
责矣。余故言其自化之功。而推及乎化国之道。欲见公之大其化也。公其勉矣夫。石泉亭记
余友柳季方筑亭广陵之野。亭之南数十武。有泉淙然出于崖石之罅者。季方顾而甚乐。名其亭曰石泉。属余为之记。余惟泉。水之本也。夫天下之水。莫盛于江海。其波涛汪潏。浴日月蒸云雨。蛇龙鹍鹏之所化。冰夷水物之变怪。歙歘闪霍。莫测其倪。甚可壮也。而其本则泉也。泉之始出。其细如丝。而其流既远。则其积自厚。而其所就也如彼。今夫君子之仕于国也。左右其君。泽降于民。不动声色而援天下于既溺。功烈溢于旂常。名声贯乎日星。是岂无所本而能之乎。人之一身。固眇然也。而其中则自有统万化而弥四海者。惟心是也。君子之业。所以洸洸然震耀耳目。盖亦本之心已矣。然心之为物也微。故苟不养而充之。则其为本也易挠。而或不能进乎大矣。然有志于一时者。有志于百年者。有志于万世者。其志也远。则其养厚。其养厚。则得失不能沮其气。夷险不能变其操。其于动也。沛然如达泉矣。季方少而坎忳。及其显而年且将老矣。然不汲汲于仕。而屏野以居。岂吾所谓有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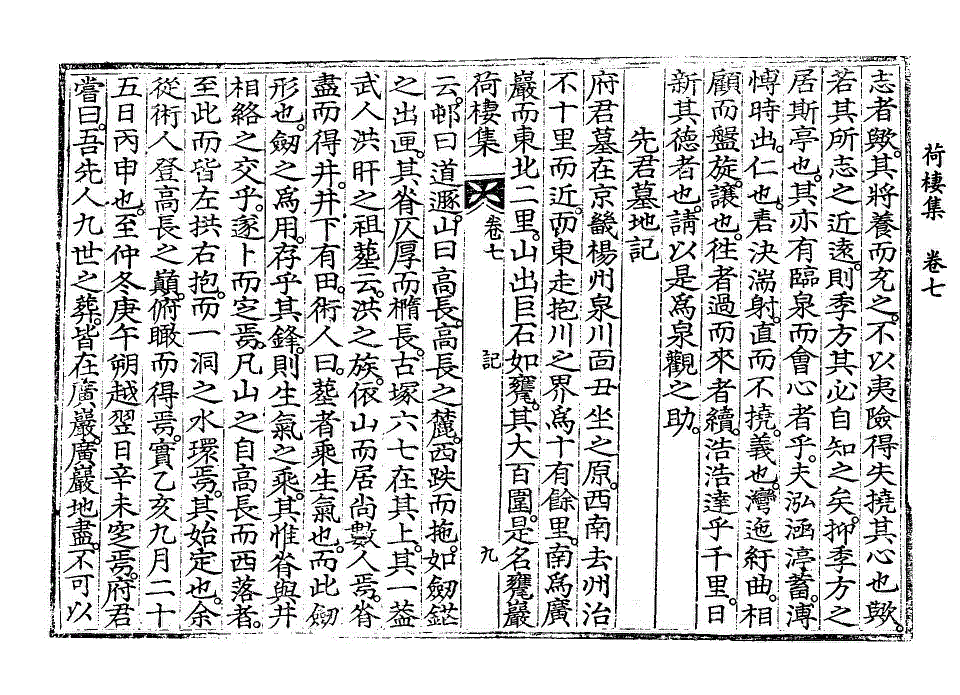 志者欤。其将养而充之。不以夷险得失挠其心也欤。若其所志之近远。则季方其必自知之矣。抑季方之居斯亭也。其亦有临泉而会心者乎。夫泓涵渟蓄。溥博时出。仁也。砉决湍射。直而不挠。义也。湾迤纡曲。相顾而盘旋。让也。往者过而来者续。浩浩达乎千里。日新其德者也。请以是为泉观之助。
志者欤。其将养而充之。不以夷险得失挠其心也欤。若其所志之近远。则季方其必自知之矣。抑季方之居斯亭也。其亦有临泉而会心者乎。夫泓涵渟蓄。溥博时出。仁也。砉决湍射。直而不挠。义也。湾迤纡曲。相顾而盘旋。让也。往者过而来者续。浩浩达乎千里。日新其德者也。请以是为泉观之助。先君墓地记
府君墓在京畿杨州泉川面丑坐之原。西南去州治不十里而近。而东走抱川之界为十有馀里。南为广岩而东北二里。山出巨石如瓮。其大百围。是名瓮岩云。村曰道遁。山曰高长。高长之麓。西跌而拖。如剑铓之出匣。其脊仄厚而椭长。古冢六七在其上。其一盖武人洪旰之祖葬云。洪之族。依山而居尚数人焉。脊尽而得井。井下有田。术人曰。葬者乘生气也。而此剑形也。剑之为用。存乎其锋。则生气之乘。其惟脊与井相络之交乎。遂卜而定焉。凡山之自高长而西落者。至此而皆左拱右抱。而一洞之水环焉。其始定也。余从术人登高长之巅。俯瞰而得焉。实乙亥九月二十五日丙申也。至仲冬庚午朔越翌日辛未窆焉。府君尝曰。吾先人九世之葬。皆在广岩。广岩地尽。不可以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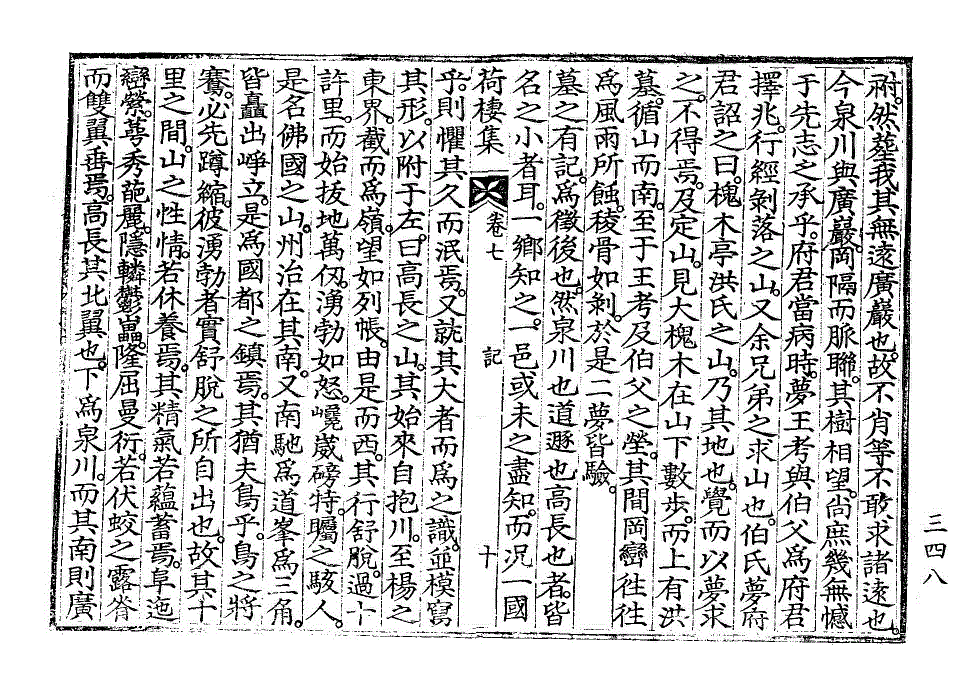 祔。然葬我其无远广岩也。故不肖等不敢求诸远也。今泉川与广岩。冈隔而脉联。其树相望。尚庶几无憾于先志之承乎。府君当病时。梦王考与伯父为府君择兆。行经剥落之山。又余兄弟之求山也。伯氏梦府君诏之曰。槐木亭洪氏之山。乃其地也。觉而以梦求之。不得焉。及定山。见大槐木在山下数步。而上有洪墓。循山而南。至于王考及伯父之茔。其间冈峦往往为风雨所蚀。棱骨如剥。于是二梦皆验。
祔。然葬我其无远广岩也。故不肖等不敢求诸远也。今泉川与广岩。冈隔而脉联。其树相望。尚庶几无憾于先志之承乎。府君当病时。梦王考与伯父为府君择兆。行经剥落之山。又余兄弟之求山也。伯氏梦府君诏之曰。槐木亭洪氏之山。乃其地也。觉而以梦求之。不得焉。及定山。见大槐木在山下数步。而上有洪墓。循山而南。至于王考及伯父之茔。其间冈峦往往为风雨所蚀。棱骨如剥。于是二梦皆验。墓之有记。为徵后也。然泉川也道遁也高长也者。皆名之小者耳。一乡知之。一邑或未之尽知。而况一国乎。则惧其久而泯焉。又就其大者而为之识。并模写其形。以附于左。曰高长之山。其始来自抱川。至杨之东界。截而为岭。望如列帐。由是而西。其行舒脱。过十许里。而始拔地万仞。涌勃如怒。巉崴磅特。瞩之骇人。是名佛国之山。州治在其南。又南驰为道峰为三角。皆矗出峥立。是为国都之镇焉。其犹夫鸟乎。鸟之将鶱。必先蹲缩。彼涌勃者实舒脱之所自出也。故其十里之间。山之性情。若休养焉。其精气若蕴蓄焉。阜迤峦萦。萼秀葩丽。隐辚郁𡾋。隆屈曼衍。若伏蛟之露脊而双翼垂焉。高长其北翼也。下为泉川。而其南则广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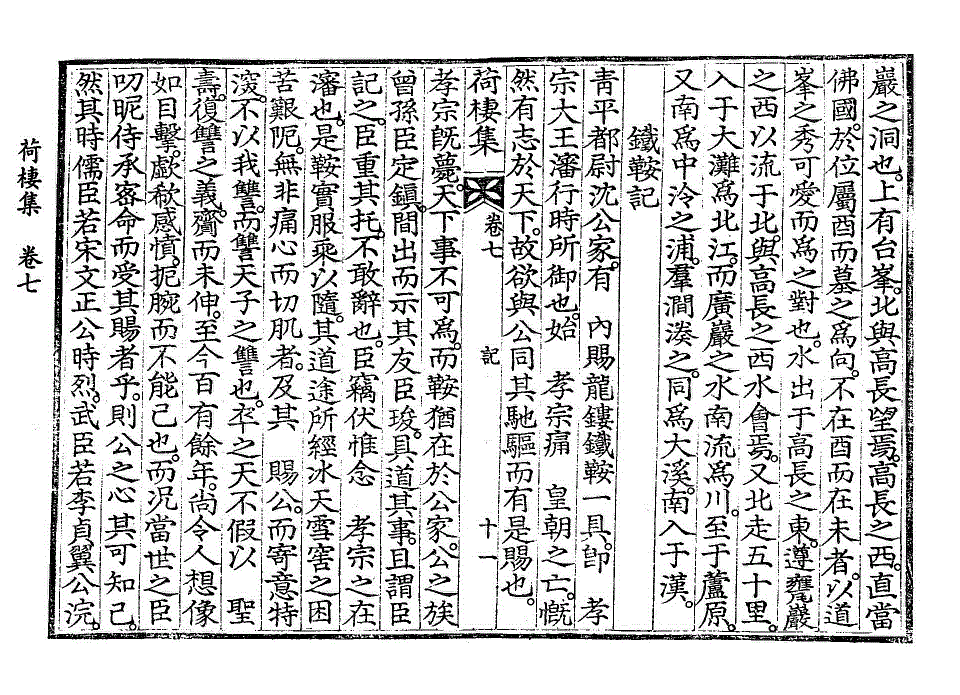 岩之洞也。上有台峰。北与高长望焉。高长之西。直当佛国。于位属酉而墓之为向。不在酉而在未者。以道峰之秀可爱而为之对也。水出于高长之东。遵瓮岩之西以流于北。与高长之西水会焉。又北走五十里。入于大滩为北江。而广岩之水南流为川。至于芦原。又南为中泠之浦。群涧凑之。同为大溪。南入于汉。
岩之洞也。上有台峰。北与高长望焉。高长之西。直当佛国。于位属酉而墓之为向。不在酉而在未者。以道峰之秀可爱而为之对也。水出于高长之东。遵瓮岩之西以流于北。与高长之西水会焉。又北走五十里。入于大滩为北江。而广岩之水南流为川。至于芦原。又南为中泠之浦。群涧凑之。同为大溪。南入于汉。铁鞍记
青平都尉沈公家。有 内赐龙镂铁鞍一具。即 孝宗大王沈行时所御也。始 孝宗痛 皇朝之亡。慨然有志于天下。故欲与公同其驰驱而有是赐也。 孝宗既薨。天下事不可为。而鞍犹在于公家。公之族曾孙臣定镇。间出而示其友臣㻐。具道其事。且谓臣记之。臣重其托。不敢辞也。臣窃伏惟念 孝宗之在沈也。是鞍实服乘以随。其道途所经冰天雪窖之困苦艰阨。无非痛心而切肌者。及其 赐公。而寄意特深。不以我雠。而雠天子之雠也。卒之天不假以 圣寿。复雠之义。赍而未伸。至今百有馀年。尚令人想像如目击。歔欷感愤。扼腕而不能已也。而况当世之臣叨昵侍承密命而受其赐者乎。则公之心其可知已。然其时儒臣若宋文正公时烈。武臣若李贞翼公浣。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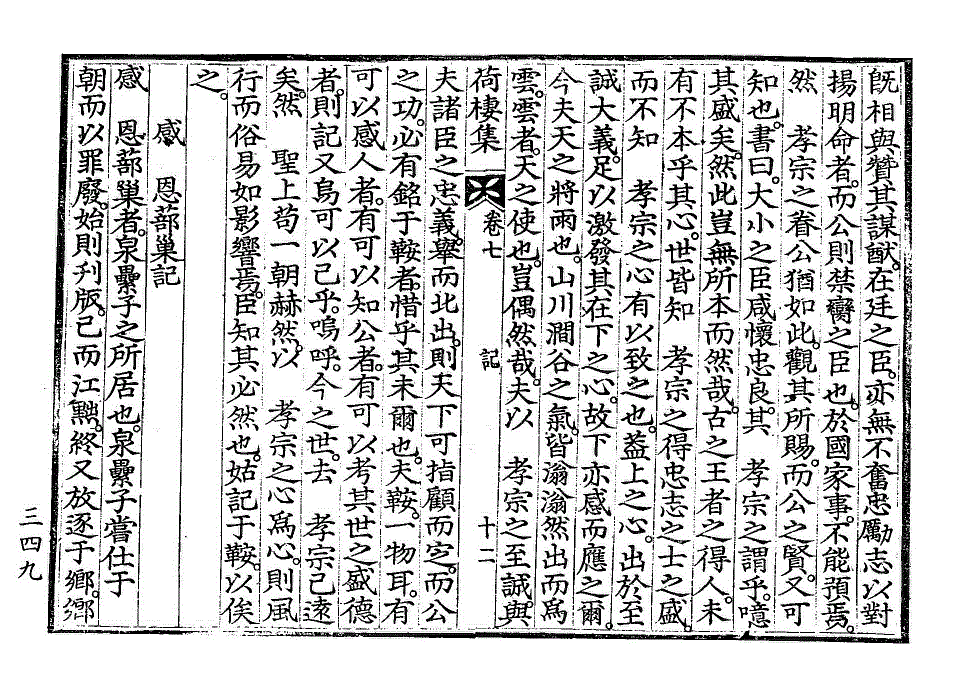 既相与赞其谋猷。在廷之臣。亦无不奋忠励志以对扬明命者。而公则禁脔之臣也。于国家事。不能预焉。然 孝宗之眷公犹如此。观其所赐。而公之贤。又可知也。书曰。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其 孝宗之谓乎。噫其盛矣。然此岂无所本而然哉。古之王者之得人。未有不本乎其心。世皆知 孝宗之得忠志之士之盛。而不知 孝宗之心有以致之也。盖上之心。出于至诚大义。足以激发其在下之心。故下亦感而应之尔。今夫天之将雨也。山川涧谷之气。皆滃滃然出而为云。云者。天之使也。岂偶然哉。夫以 孝宗之至诚。与夫诸臣之忠义。举而北出。则天下可指顾而定。而公之功。必有铭于鞍者。惜乎其未尔也。夫鞍。一物耳。有可以感人者。有可以知公者。有可以考其世之盛德者。则记又乌可以已乎。呜呼。今之世。去 孝宗已远矣。然 圣上苟一朝赫然。以 孝宗之心为心。则风行而俗易如影响焉。臣知其必然也。姑记于鞍。以俟之。
既相与赞其谋猷。在廷之臣。亦无不奋忠励志以对扬明命者。而公则禁脔之臣也。于国家事。不能预焉。然 孝宗之眷公犹如此。观其所赐。而公之贤。又可知也。书曰。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其 孝宗之谓乎。噫其盛矣。然此岂无所本而然哉。古之王者之得人。未有不本乎其心。世皆知 孝宗之得忠志之士之盛。而不知 孝宗之心有以致之也。盖上之心。出于至诚大义。足以激发其在下之心。故下亦感而应之尔。今夫天之将雨也。山川涧谷之气。皆滃滃然出而为云。云者。天之使也。岂偶然哉。夫以 孝宗之至诚。与夫诸臣之忠义。举而北出。则天下可指顾而定。而公之功。必有铭于鞍者。惜乎其未尔也。夫鞍。一物耳。有可以感人者。有可以知公者。有可以考其世之盛德者。则记又乌可以已乎。呜呼。今之世。去 孝宗已远矣。然 圣上苟一朝赫然。以 孝宗之心为心。则风行而俗易如影响焉。臣知其必然也。姑记于鞍。以俟之。感 恩蔀巢记
感 恩蔀巢者。泉累子之所居也。泉累子尝仕于 朝而以罪废。始则刊版。已而江黜。终又放逐于乡。乡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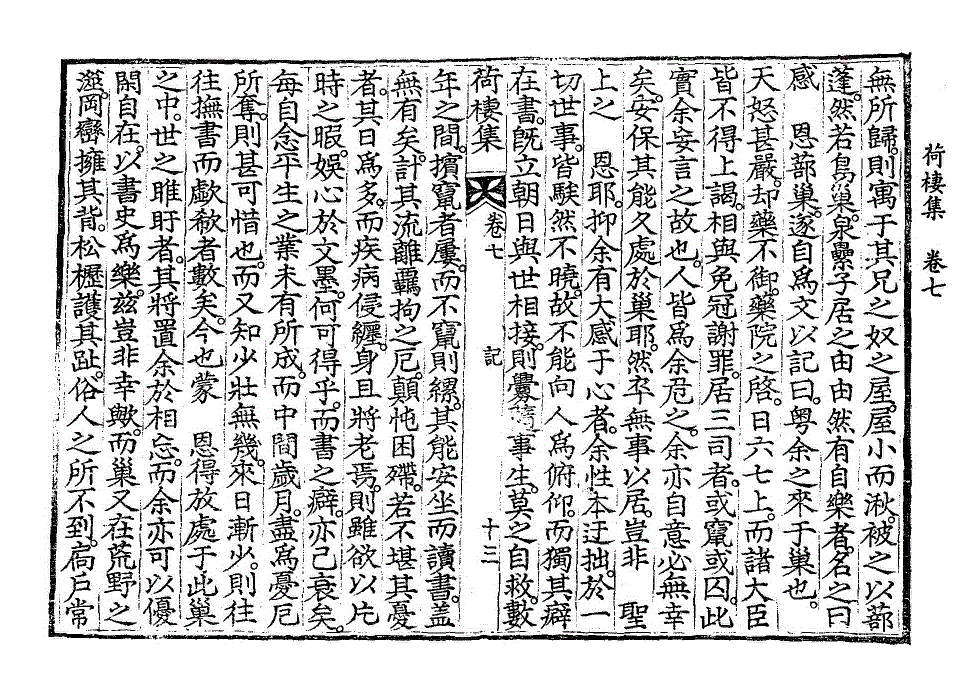 无所归。则寓于其兄之奴之屋。屋小而湫。被之以蔀蓬。然若鸟巢。泉累子居之由由然有自乐者。名之曰感 恩蔀巢。遂自为文以记曰。粤余之来于巢也。 天怒甚严。却药不御。药院之启。日六七上。而诸大臣皆不得上谒。相与免冠谢罪。居三司者。或窜或囚。此实余妄言之故也。人皆为余危之。余亦自意必无幸矣。安保其能久处于巢耶。然卒无事以居。岂非 圣上之 恩耶。抑余有大感于心者。余性本迂拙。于一切世事。皆騃然不晓。故不能向人为俯仰。而独其癖在书。既立朝日与世相接。则衅随事生。莫之自救。数年之间。摈窜者屡。而不窜则缧。其能安坐而读书。盖无有矣。计其流离羁拘之厄。颠忳困殢。若不堪其忧者。其日为多。而疾病侵缠。身且将老焉。则虽欲以片时之暇。娱心于文墨。何可得乎。而书之癖。亦已衰矣。每自念平生之业未有所成。而中间岁月。尽为忧厄所夺。则甚可惜也。而又知少壮无几。来日渐少。则往往抚书而歔欷者数矣。今也蒙 恩得放处于此巢之中。世之睢盱者。其将置余于相忘。而余亦可以优闲自在。以书史为乐。玆岂非幸欤。而巢又在荒野之澨。冈峦拥其背。松枥护其趾。俗人之所不到。扃户常
无所归。则寓于其兄之奴之屋。屋小而湫。被之以蔀蓬。然若鸟巢。泉累子居之由由然有自乐者。名之曰感 恩蔀巢。遂自为文以记曰。粤余之来于巢也。 天怒甚严。却药不御。药院之启。日六七上。而诸大臣皆不得上谒。相与免冠谢罪。居三司者。或窜或囚。此实余妄言之故也。人皆为余危之。余亦自意必无幸矣。安保其能久处于巢耶。然卒无事以居。岂非 圣上之 恩耶。抑余有大感于心者。余性本迂拙。于一切世事。皆騃然不晓。故不能向人为俯仰。而独其癖在书。既立朝日与世相接。则衅随事生。莫之自救。数年之间。摈窜者屡。而不窜则缧。其能安坐而读书。盖无有矣。计其流离羁拘之厄。颠忳困殢。若不堪其忧者。其日为多。而疾病侵缠。身且将老焉。则虽欲以片时之暇。娱心于文墨。何可得乎。而书之癖。亦已衰矣。每自念平生之业未有所成。而中间岁月。尽为忧厄所夺。则甚可惜也。而又知少壮无几。来日渐少。则往往抚书而歔欷者数矣。今也蒙 恩得放处于此巢之中。世之睢盱者。其将置余于相忘。而余亦可以优闲自在。以书史为乐。玆岂非幸欤。而巢又在荒野之澨。冈峦拥其背。松枥护其趾。俗人之所不到。扃户常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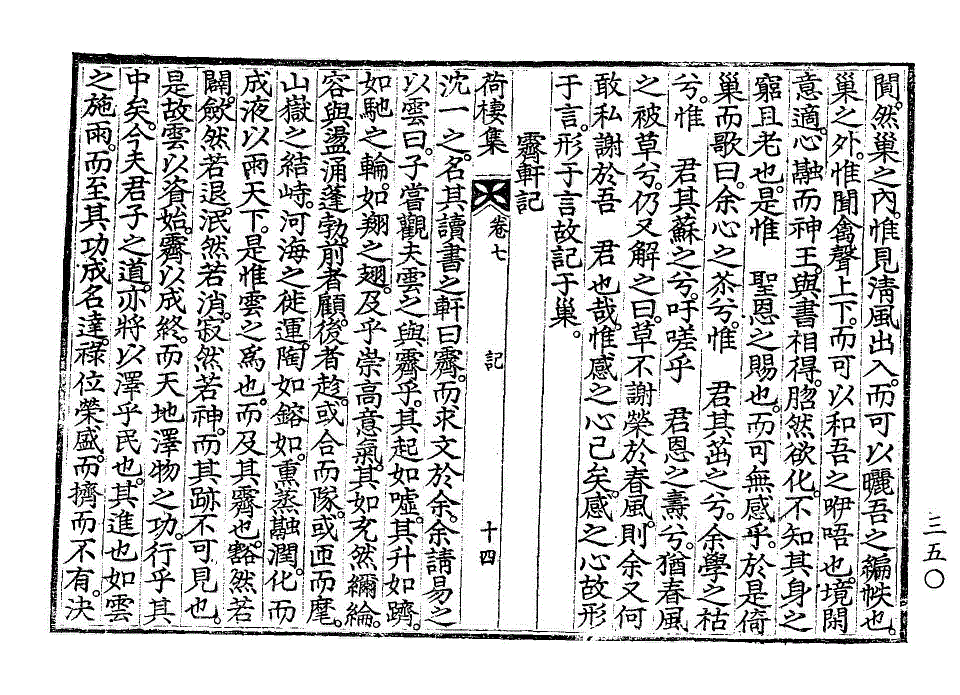 阒。然巢之内。惟见清风出入。而可以晒吾之编帙也。巢之外。惟闻禽声上下。而可以和吾之咿唔也。境闲意适。心融而神王。与书相得。吻然欲化。不知其身之穷且老也。是惟 圣恩之赐也。而可无感乎。于是倚巢而歌曰。余心之苶兮。惟 君其茁之兮。余学之枯兮。惟 君其苏之兮。吁嗟乎 君恩之焘兮。犹春风之被草兮。仍又解之曰。草不谢荣于春风。则余又何敢私谢于吾 君也哉。惟感之心已矣。感之心故形于言。形于言故记于巢。
阒。然巢之内。惟见清风出入。而可以晒吾之编帙也。巢之外。惟闻禽声上下。而可以和吾之咿唔也。境闲意适。心融而神王。与书相得。吻然欲化。不知其身之穷且老也。是惟 圣恩之赐也。而可无感乎。于是倚巢而歌曰。余心之苶兮。惟 君其茁之兮。余学之枯兮。惟 君其苏之兮。吁嗟乎 君恩之焘兮。犹春风之被草兮。仍又解之曰。草不谢荣于春风。则余又何敢私谢于吾 君也哉。惟感之心已矣。感之心故形于言。形于言故记于巢。霁轩记
沈一之。名其读书之轩曰霁。而求文于余。余请易之以云曰。子尝观夫云之与霁乎。其起如嘘。其升如跻。如驰之轮。如翔之翅。及乎崇高意气。其如充然䌤纶。容与荡涌蓬勃。前者顾。后者趁。或合而队。或匝而麾。山岳之结峙。河海之徙运。陶如镕如。熏蒸融润。化而成液以雨天下。是惟云之为也。而及其霁也。豁然若辟。敛然若退。泯然若消。寂然若神。而其迹不可见也。是故云以资始。霁以成终。而天地泽物之功。行乎其中矣。今夫君子之道。亦将以泽乎民也。其进也如云之施雨。而至其功成名达。禄位荣盛。而挤而不有。决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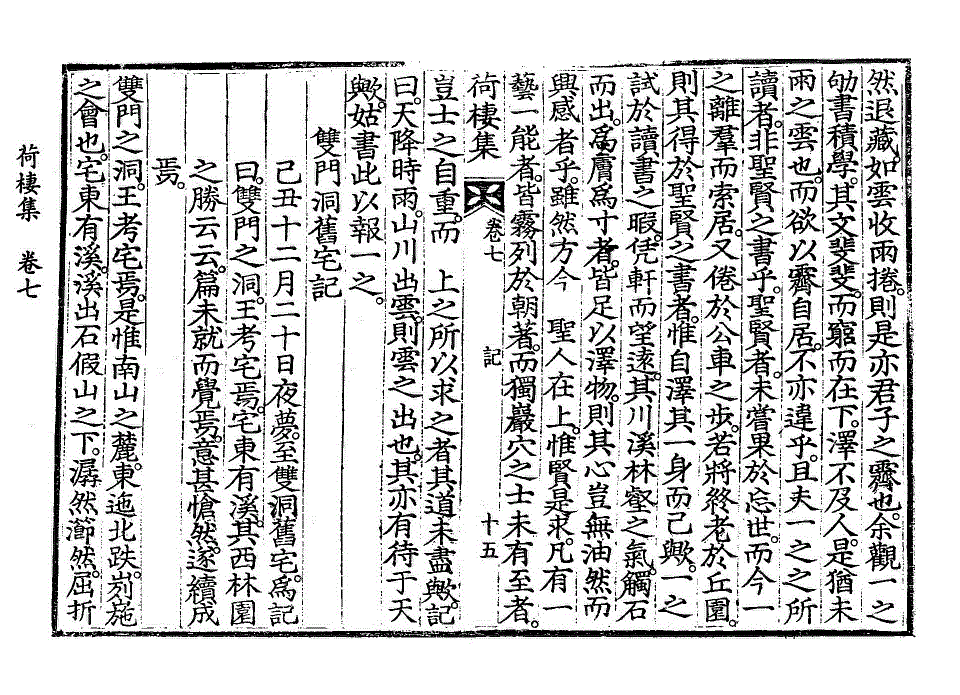 然退藏。如云收雨捲。则是亦君子之霁也。余观一之劬书积学。其文斐斐。而穷而在下。泽不及人。是犹未雨之云也。而欲以霁自居。不亦违乎。且夫一之之所读者。非圣贤之书乎。圣贤者。未尝果于忘世。而今一之离群而索居。又倦于公车之步。若将终老于丘园。则其得于圣贤之书者。惟自泽其一身而已欤。一之试于读书之暇。凭轩而望远。其川溪林壑之气。触石而出。为肤为寸者。皆足以泽物。则其心岂无油然而兴感者乎。虽然方今 圣人在上。惟贤是求。凡有一艺一能者。皆雾列于朝著。而独岩穴之士未有至者。岂士之自重。而 上之所以求之者其道未尽欤。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则云之出也。其亦有待于天欤。姑书此以报一之。
然退藏。如云收雨捲。则是亦君子之霁也。余观一之劬书积学。其文斐斐。而穷而在下。泽不及人。是犹未雨之云也。而欲以霁自居。不亦违乎。且夫一之之所读者。非圣贤之书乎。圣贤者。未尝果于忘世。而今一之离群而索居。又倦于公车之步。若将终老于丘园。则其得于圣贤之书者。惟自泽其一身而已欤。一之试于读书之暇。凭轩而望远。其川溪林壑之气。触石而出。为肤为寸者。皆足以泽物。则其心岂无油然而兴感者乎。虽然方今 圣人在上。惟贤是求。凡有一艺一能者。皆雾列于朝著。而独岩穴之士未有至者。岂士之自重。而 上之所以求之者其道未尽欤。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则云之出也。其亦有待于天欤。姑书此以报一之。双门洞旧宅记
己丑十二月二十日夜梦。至双洞旧宅。为记曰。双门之洞。王考宅焉。宅东有溪。其西林园之胜云云。篇未就而觉焉。意甚怆然。遂续成焉。
双门之洞。王考宅焉。是惟南山之麓。东迤北跌。峛崺之会也。宅东有溪。溪出石假山之下。潺然瀄然。屈折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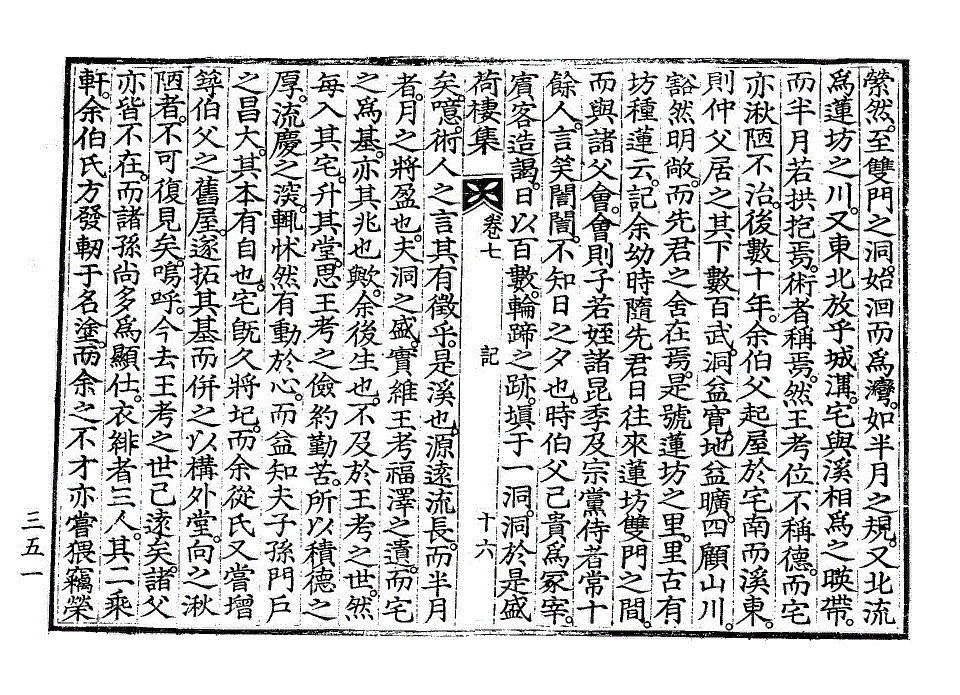 萦然。至双门之洞。始洄而为湾。如半月之规。又北流为莲坊之川。又东北放乎城沟。宅与溪相为之映带。而半月若拱抱焉。术者称焉。然王考位不称德。而宅亦湫陋不治。后数十年。余伯父起屋于宅南而溪东。则仲父居之其下数百武。洞益宽。地益旷。四顾山川。豁然明敞。而先君之舍在焉。是号莲坊之里。里古有坊种莲云。记余幼时随先君日往来莲坊双门之间。而与诸父会。会则子若侄诸昆季及宗党侍者常十馀人。言笑訚訚。不知日之夕也。时伯父已贵为冢宰。宾客造谒。日以百数。轮蹄之迹。填于一洞。洞于是盛矣。噫。术人之言其有徵乎。是溪也。源远流长。而半月者。月之将盈也。夫洞之盛。实维王考福泽之遗。而宅之为基。亦其兆也欤。余后生也。不及于王考之世。然每入其宅。升其堂。思王考之俭约勤苦。所以积德之厚。流庆之深。辄怵然有动于心。而益知夫子孙门户之昌大。其本有自也。宅既久将圮。而余从氏又尝增筑伯父之旧屋。遂拓其基而并之以构外堂。向之湫陋者。不可复见矣。呜呼。今去王考之世已远矣。诸父亦皆不在。而诸孙尚多为显仕。衣绯者三人。其二乘轩。余伯氏方发轫于名涂。而余之不才亦尝猥窃荣
萦然。至双门之洞。始洄而为湾。如半月之规。又北流为莲坊之川。又东北放乎城沟。宅与溪相为之映带。而半月若拱抱焉。术者称焉。然王考位不称德。而宅亦湫陋不治。后数十年。余伯父起屋于宅南而溪东。则仲父居之其下数百武。洞益宽。地益旷。四顾山川。豁然明敞。而先君之舍在焉。是号莲坊之里。里古有坊种莲云。记余幼时随先君日往来莲坊双门之间。而与诸父会。会则子若侄诸昆季及宗党侍者常十馀人。言笑訚訚。不知日之夕也。时伯父已贵为冢宰。宾客造谒。日以百数。轮蹄之迹。填于一洞。洞于是盛矣。噫。术人之言其有徵乎。是溪也。源远流长。而半月者。月之将盈也。夫洞之盛。实维王考福泽之遗。而宅之为基。亦其兆也欤。余后生也。不及于王考之世。然每入其宅。升其堂。思王考之俭约勤苦。所以积德之厚。流庆之深。辄怵然有动于心。而益知夫子孙门户之昌大。其本有自也。宅既久将圮。而余从氏又尝增筑伯父之旧屋。遂拓其基而并之以构外堂。向之湫陋者。不可复见矣。呜呼。今去王考之世已远矣。诸父亦皆不在。而诸孙尚多为显仕。衣绯者三人。其二乘轩。余伯氏方发轫于名涂。而余之不才亦尝猥窃荣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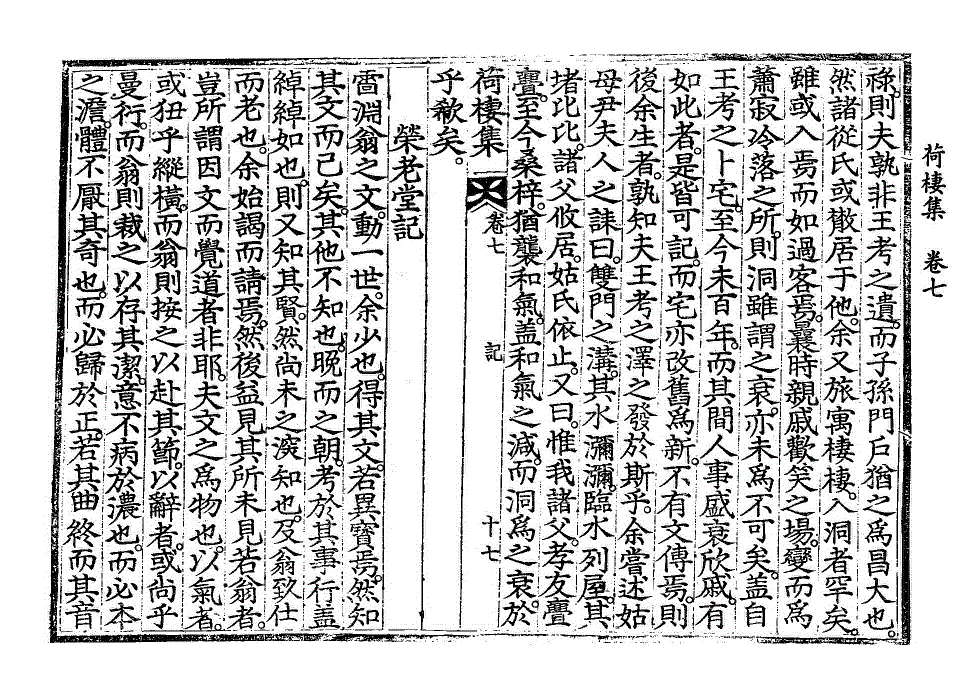 禄。则夫孰非王考之遗。而子孙门户犹之为昌大也。然诸从氏或散居于他。余又旅寓栖栖。入洞者罕矣。虽或入焉而如过客焉。曩时亲戚欢笑之场。变而为萧寂冷落之所。则洞虽谓之衰。亦未为不可矣。盖自王考之卜宅。至今未百年。而其间人事盛衰欣戚。有如此者。是皆可记。而宅亦改旧为新。不有文传焉。则后余生者。孰知夫王考之泽之发于斯乎。余尝述姑母尹夫人之诔曰。双门之沟。其水㳽㳽。临水列屋。其堵比比。诸父攸居。姑氏依止。又曰。惟我诸父。孝友亹亹。至今桑梓。犹袭和气。盖和气之减。而洞为之衰。于乎欷矣。
禄。则夫孰非王考之遗。而子孙门户犹之为昌大也。然诸从氏或散居于他。余又旅寓栖栖。入洞者罕矣。虽或入焉而如过客焉。曩时亲戚欢笑之场。变而为萧寂冷落之所。则洞虽谓之衰。亦未为不可矣。盖自王考之卜宅。至今未百年。而其间人事盛衰欣戚。有如此者。是皆可记。而宅亦改旧为新。不有文传焉。则后余生者。孰知夫王考之泽之发于斯乎。余尝述姑母尹夫人之诔曰。双门之沟。其水㳽㳽。临水列屋。其堵比比。诸父攸居。姑氏依止。又曰。惟我诸父。孝友亹亹。至今桑梓。犹袭和气。盖和气之减。而洞为之衰。于乎欷矣。荣老堂记
䨓渊翁之文。动一世。余少也。得其文。若异宝焉。然知其文而已矣。其他不知也。晚而之朝。考于其事行盖绰绰如也。则又知其贤。然尚未之深知也。及翁致仕而老也。余始谒而请焉。然后益见其所未见若翁者。岂所谓因文而觉道者非耶。夫文之为物也。以气者。或狃乎纵横。而翁则按之以赴其节。以辞者。或尚乎曼衍。而翁则裁之以存其洁。意不病于浓也。而必本之澹。体不厌其奇也。而必归于正。若其曲终而其音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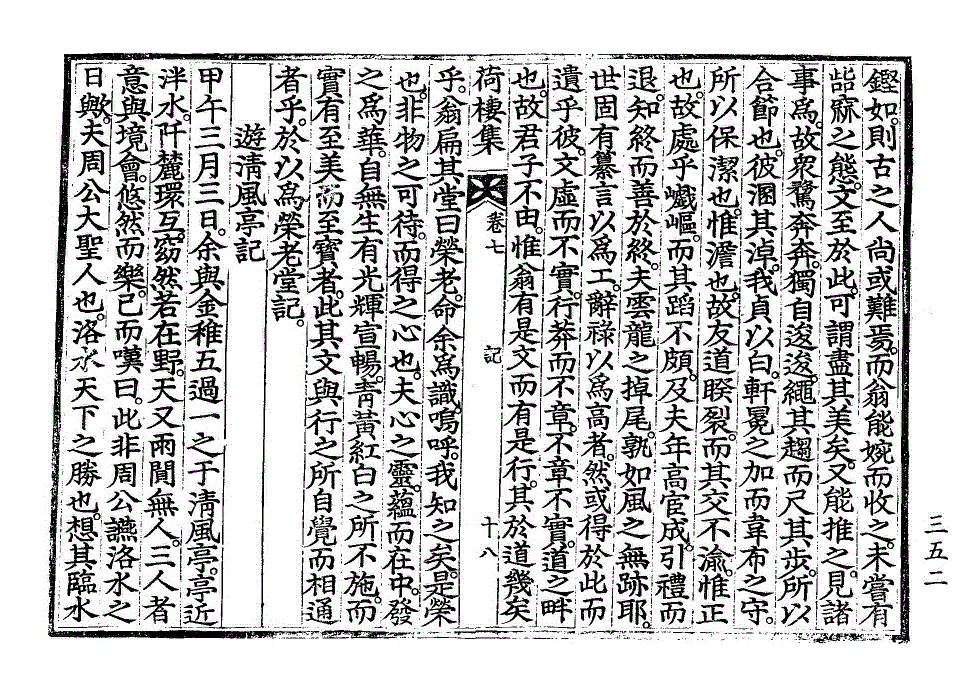 铿如。则古之人尚或难焉。而翁能婉而收之。未尝有啙窳之态。文至于此。可谓尽其美矣。又能推之。见诸事为。故众骛奔奔。独自逡逡。绳其趋而尺其步。所以合节也。彼溷其淖。我贞以白。轩冕之加而韦布之守。所以保洁也。惟澹也。故友道睽裂。而其交不渝。惟正也。故处乎𡾟岖。而其蹈不颇。及夫年高宦成。引礼而退。知终而善于终。夫云龙之掉尾。孰如风之无迹耶。世固有纂言以为工。辞禄以为高者。然或得于此而遗乎彼。文虚而不实。行莽而不章。不章不实。道之畔也。故君子不由。惟翁有是文而有是行。其于道几矣乎。翁扁其堂曰荣老。命余为识。呜呼。我知之矣。是荣也。非物之可待。而得之心也。夫心之灵。蕴而在中。发之为华。自无生有光辉宣畅。青黄红白之所不施。而实有至美而至宝者。此其文与行之所自觉而相通者乎。于以为荣老堂记。
铿如。则古之人尚或难焉。而翁能婉而收之。未尝有啙窳之态。文至于此。可谓尽其美矣。又能推之。见诸事为。故众骛奔奔。独自逡逡。绳其趋而尺其步。所以合节也。彼溷其淖。我贞以白。轩冕之加而韦布之守。所以保洁也。惟澹也。故友道睽裂。而其交不渝。惟正也。故处乎𡾟岖。而其蹈不颇。及夫年高宦成。引礼而退。知终而善于终。夫云龙之掉尾。孰如风之无迹耶。世固有纂言以为工。辞禄以为高者。然或得于此而遗乎彼。文虚而不实。行莽而不章。不章不实。道之畔也。故君子不由。惟翁有是文而有是行。其于道几矣乎。翁扁其堂曰荣老。命余为识。呜呼。我知之矣。是荣也。非物之可待。而得之心也。夫心之灵。蕴而在中。发之为华。自无生有光辉宣畅。青黄红白之所不施。而实有至美而至宝者。此其文与行之所自觉而相通者乎。于以为荣老堂记。游清风亭记
甲午三月三日。余与金稚五过一之于清风亭。亭近泮水。阡麓环互。窈然若在野。天又雨阒无人。三人者意与境会。悠然而乐。已而叹曰。此非周公宴洛水之日欤。夫周公大圣人也。洛水天下之胜也。想其临水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3H 页
 而宴也。尚父授几。召公肆筵。𩱛迈之工。无非正士。其乐何如也。故其诗曰。羽觞随波。今吾三人者之会。适在是日。岂不奇乎哉。然世远千岁。地不尽万里。而我又未免为乡人。则安得不有感焉者乎。夫日周乎天而感在于心。日之所临。感随而生。日果不可无待也。然唐晋天津兰亭之游。游于是日。而只以笔诗鸣。曾点氏浴沂风雩。未必是日之游。而夫子与之。其果待于日欤。日不可苟同也。我辈盍因其所同而益求其进也哉。既罢。一之属余为记。是日三人者谭文章。稚五曰。吾于圣人之文所独嗜者。论语也。余则曰。其易爻之繇乎。一之方读仪礼。皆周,孔之书也。又若有不偶然者。并记之。
而宴也。尚父授几。召公肆筵。𩱛迈之工。无非正士。其乐何如也。故其诗曰。羽觞随波。今吾三人者之会。适在是日。岂不奇乎哉。然世远千岁。地不尽万里。而我又未免为乡人。则安得不有感焉者乎。夫日周乎天而感在于心。日之所临。感随而生。日果不可无待也。然唐晋天津兰亭之游。游于是日。而只以笔诗鸣。曾点氏浴沂风雩。未必是日之游。而夫子与之。其果待于日欤。日不可苟同也。我辈盍因其所同而益求其进也哉。既罢。一之属余为记。是日三人者谭文章。稚五曰。吾于圣人之文所独嗜者。论语也。余则曰。其易爻之繇乎。一之方读仪礼。皆周,孔之书也。又若有不偶然者。并记之。荷栖集卷之七
题跋
题泣蓼编世谱后
呜呼。此吾先君世谱也。粤惟侍中公笃阀启姓。世其有家。而其显于我 朝。实自恭肃公始。恭肃之后。四世三显。及景穆公之有社稷勋。则谱于是益显。尤庵宋先生尝曰。我国赵氏。系出丰壤者为显。而景穆之家。又为丰壤之显者。景穆公。先君之曾祖也。诗不云乎。不显亦世。盖言德也。吾门累世之显。夫岂无自而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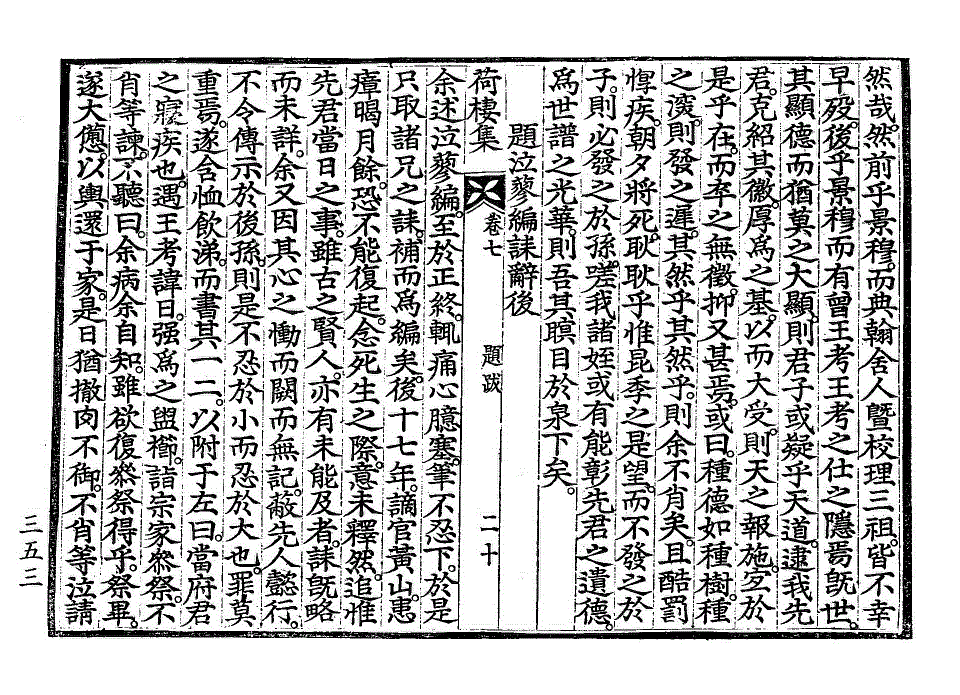 然哉。然前乎景穆。而典翰舍人暨校理三祖。皆不幸早殁。后乎景穆而有曾王考王考之仕之隐焉既世。其显德而犹莫之大显。则君子或疑乎天道。逮我先君。克绍其徽。厚为之基。以而大受。则天之报施。宜于是乎在。而卒之无徵。抑又甚焉。或曰。种德如种树。种之深。则发之迟。其然乎其然乎。则余不肖矣。且酷罚茕疾。朝夕将死。耿耿乎惟昆季之是望。而不发之于子。则必发之于孙。嗟我诸侄或有能彰先君之遗德。为世谱之光华。则吾其瞑目于泉下矣。
然哉。然前乎景穆。而典翰舍人暨校理三祖。皆不幸早殁。后乎景穆而有曾王考王考之仕之隐焉既世。其显德而犹莫之大显。则君子或疑乎天道。逮我先君。克绍其徽。厚为之基。以而大受。则天之报施。宜于是乎在。而卒之无徵。抑又甚焉。或曰。种德如种树。种之深。则发之迟。其然乎其然乎。则余不肖矣。且酷罚茕疾。朝夕将死。耿耿乎惟昆季之是望。而不发之于子。则必发之于孙。嗟我诸侄或有能彰先君之遗德。为世谱之光华。则吾其瞑目于泉下矣。题泣蓼编诔辞后
余述泣蓼编。至于正终。辄痛心臆塞。笔不忍下。于是只取诸兄之诔。补而为编矣。后十七年。谪官黄山。患瘴暍月馀。恐不能复起。念死生之际。意未释然。追惟先君当日之事。虽古之贤人。亦有未能及者。诔既略而未详。余又因其心之恸而阙而无记。蔽先人懿行。不令传示于后孙。则是不忍于小而忍于大也。罪莫重焉。遂含恤饮涕。而书其一二。以附于左曰。当府君之寝疾也。遇王考讳日。强为之盥栉。诣宗家参祭。不肖等谏。不听曰。余病余自知。虽欲复参祭得乎。祭毕。遂大惫。以舆还于家。是日犹撤肉不御。不肖等泣请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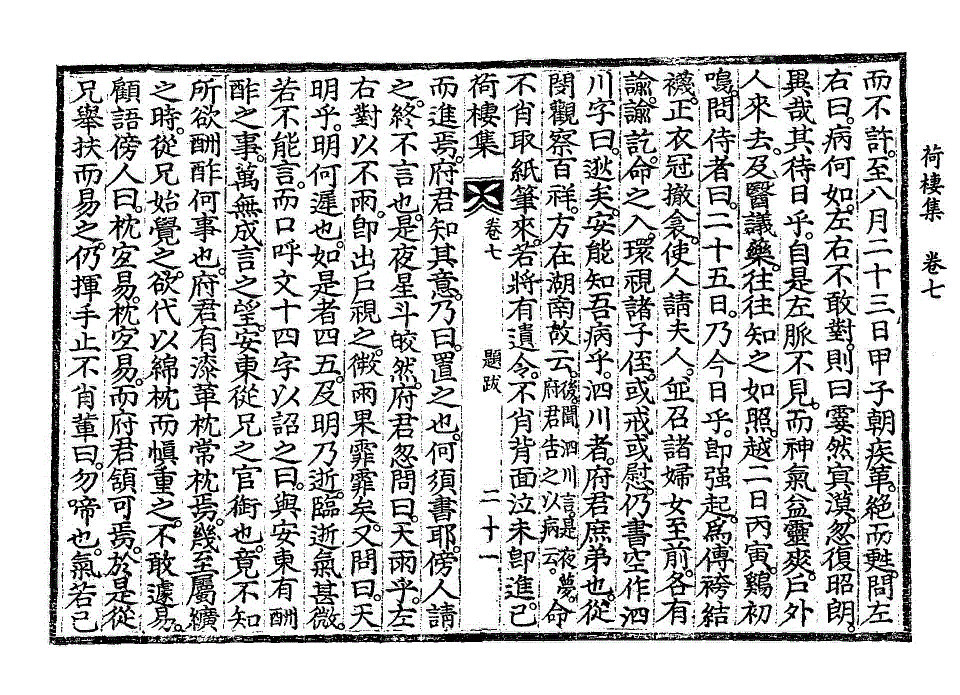 而不许。至八月二十三日甲子朝疾革。绝而苏。问左右曰。病何如。左右不敢对。则曰霎然冥漠。忽复昭朗。异哉其待日乎。自是左脉不见。而神气益灵爽。户外人来去。及医议药。往往知之如照。越二日丙寅。鸡初鸣。问侍者曰。二十五日。乃今日乎。即强起。为傅裤结袜。正衣冠撤衾。使人请夫人。并召诸妇女至前。各有谕。谕讫。命之入。环视诸子侄。或戒或慰。仍书空作泗川字曰。逖矣。安能知吾病乎。泗川者。府君庶弟也。从闵观察百祥。方在湖南故云。(后。闻泗川言。是夜梦。府君告之以病云。)命不肖取纸笔来。若将有遗令。不肖背面泣未即进。已而进焉。府君知其意。乃曰。置之也。何须书耶。傍人请之。终不言也。是夜星斗皎然。府君忽问曰。天雨乎。左右对以不雨。即出户视之。微雨果霏霏矣。又问曰。天明乎。明何迟也。如是者四五。及明乃逝。临逝气甚微。若不能言。而口呼文十四字以诏之曰。与安东有酬酢之事。万无成言之望。安东从兄之官衔也。竟不知所欲酬酢何事也。府君有漆革枕常枕焉。几至属纩之时。从兄始觉之。欲代以绵枕而慎重之。不敢遽易。顾语傍人曰。枕宜易。枕宜易。而府君颔可焉。于是从兄举扶而易之。仍挥手止不肖辈曰。勿啼也。气若已
而不许。至八月二十三日甲子朝疾革。绝而苏。问左右曰。病何如。左右不敢对。则曰霎然冥漠。忽复昭朗。异哉其待日乎。自是左脉不见。而神气益灵爽。户外人来去。及医议药。往往知之如照。越二日丙寅。鸡初鸣。问侍者曰。二十五日。乃今日乎。即强起。为傅裤结袜。正衣冠撤衾。使人请夫人。并召诸妇女至前。各有谕。谕讫。命之入。环视诸子侄。或戒或慰。仍书空作泗川字曰。逖矣。安能知吾病乎。泗川者。府君庶弟也。从闵观察百祥。方在湖南故云。(后。闻泗川言。是夜梦。府君告之以病云。)命不肖取纸笔来。若将有遗令。不肖背面泣未即进。已而进焉。府君知其意。乃曰。置之也。何须书耶。傍人请之。终不言也。是夜星斗皎然。府君忽问曰。天雨乎。左右对以不雨。即出户视之。微雨果霏霏矣。又问曰。天明乎。明何迟也。如是者四五。及明乃逝。临逝气甚微。若不能言。而口呼文十四字以诏之曰。与安东有酬酢之事。万无成言之望。安东从兄之官衔也。竟不知所欲酬酢何事也。府君有漆革枕常枕焉。几至属纩之时。从兄始觉之。欲代以绵枕而慎重之。不敢遽易。顾语傍人曰。枕宜易。枕宜易。而府君颔可焉。于是从兄举扶而易之。仍挥手止不肖辈曰。勿啼也。气若已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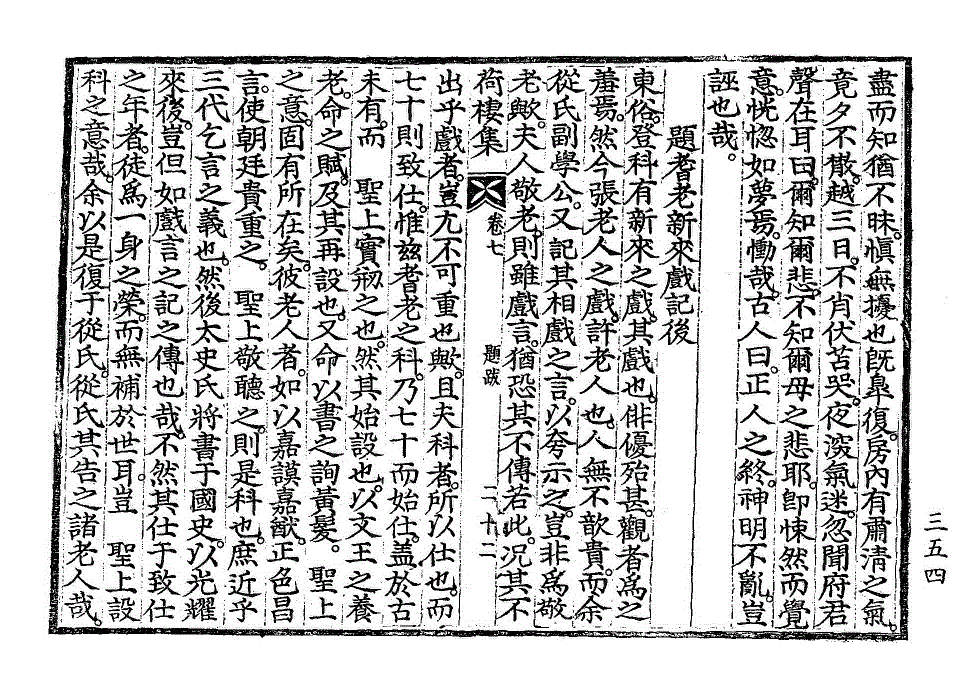 尽而知犹不昧。慎无扰也既皋复。房内有肃清之气。竟夕不散。越三日。不肖伏苫哭。夜深气迷。忽闻府君声在耳曰。尔知尔悲。不知尔母之悲耶。即悚然而觉意。恍惚如梦焉。恸哉。古人曰。正人之终。神明不乱。岂诬也哉。
尽而知犹不昧。慎无扰也既皋复。房内有肃清之气。竟夕不散。越三日。不肖伏苫哭。夜深气迷。忽闻府君声在耳曰。尔知尔悲。不知尔母之悲耶。即悚然而觉意。恍惚如梦焉。恸哉。古人曰。正人之终。神明不乱。岂诬也哉。题耆老新来戏记后
东俗。登科有新来之戏。其戏也。俳优殆甚。观者为之羞焉。然今张老人之戏。许老人也。人无不歆贵。而余从氏副学公。又记其相戏之言。以夸示之。岂非为敬老欤。夫人敬老。则虽戏言。犹恐其不传若此。况其不出乎戏者。岂尤不可重也欤。且夫科者。所以仕也。而七十则致仕。惟玆耆老之科。乃七十而始仕。盖于古未有。而 圣上实刱之也。然其始设也。以文王之养老。命之赋。及其再设也。又命以书之询黄发。 圣上之意。固有所在矣。彼老人者。如以嘉谟嘉猷。正色昌言。使朝廷贵重之。 圣上敬听之。则是科也。庶近乎三代乞言之义也。然后太史氏将书于国史。以光耀来后。岂但如戏言之记之传也哉。不然其仕于致仕之年者。徒为一身之荣。而无补于世耳。岂 圣上设科之意哉。余以是复于从氏。从氏其告之诸老人哉。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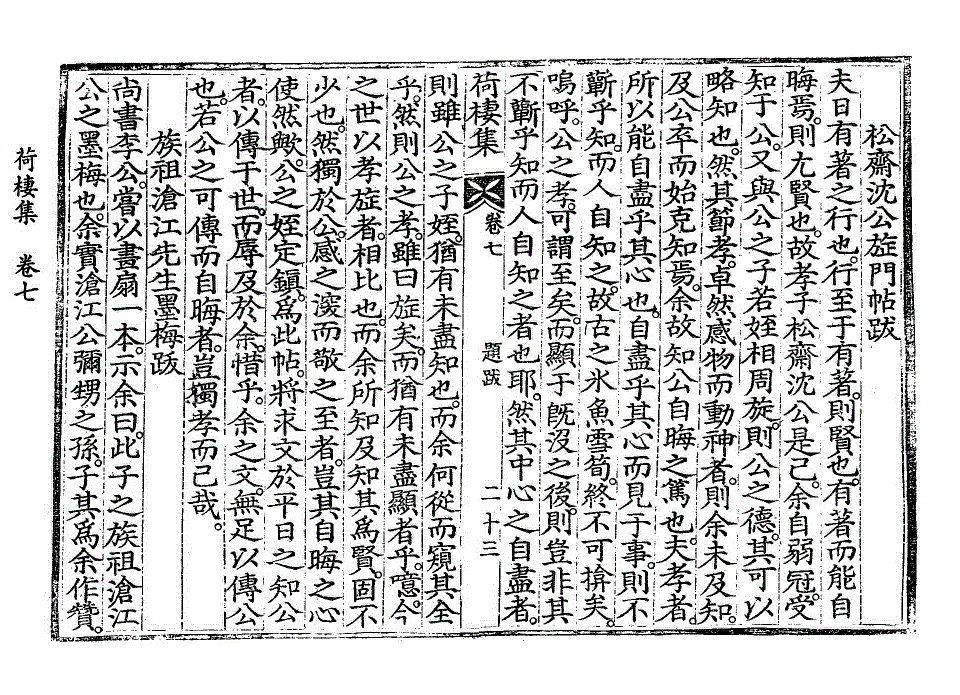 松斋沈公旌门帖跋
松斋沈公旌门帖跋夫日有著之行也。行至于有著。则贤也。有著而能自晦焉。则尤贤也。故孝子松斋沈公是已。余自弱冠。受知于公。又与公之子若侄相周旋。则公之德。其可以略知也。然其节孝。卓然感物而动神者。则余未及知。及公卒而始克知焉。余故知公自晦之笃也。夫孝者。所以能自尽乎其心也。自尽乎其心而见于事。则不蕲乎知。而人自知之。故古之冰鱼雪笋。终不可掩矣。呜呼。公之孝。可谓至矣。而显于既没之后。则岂非其不蕲乎知而人自知之者也耶。然其中心之自尽者。则虽公之子侄。犹有未尽知也。而余何从而窥其全乎。然则公之孝。虽曰旌矣。而犹有未尽显者乎。噫。今之世以孝旌者。相比也。而余所知及知其为贤。固不少也。然独于公。感之深而敬之至者。岂其自晦之心使然欤。公之侄定镇。为此帖。将求文于平日之知公者。以传于世。而辱及于余。惜乎。余之文。无足以传公也。若公之可传而自晦者。岂独孝而已哉。
族祖沧江先生墨梅跋
尚书李公。尝以画扇一本。示余曰。此子之族祖沧江公之墨梅也。余实沧江公弥甥之孙。子其为余作赞。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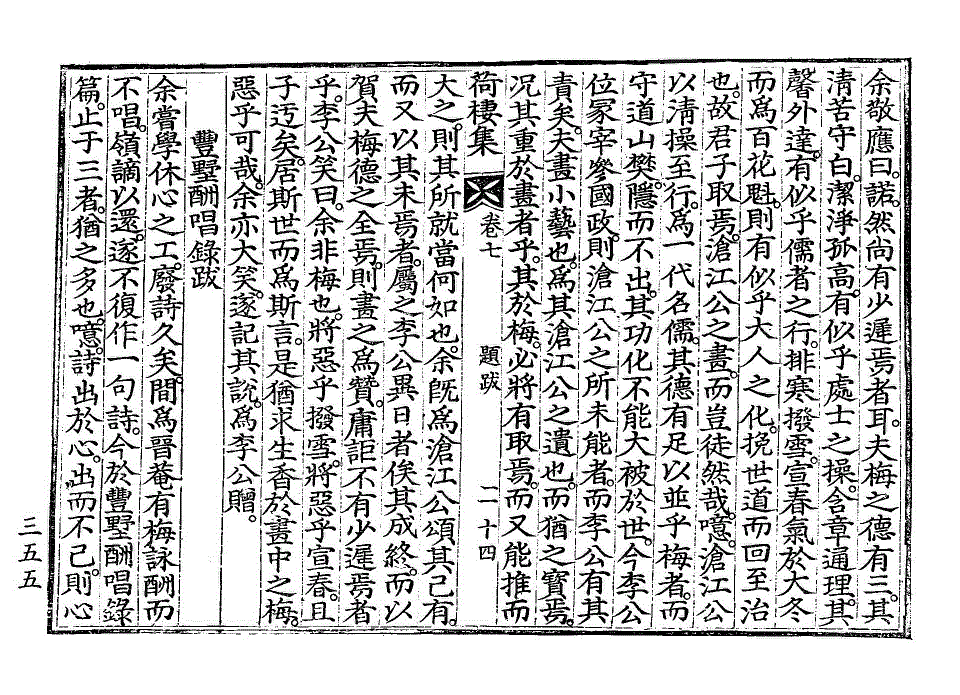 余敬应曰。诺。然尚有少迟焉者耳。夫梅之德有三。其清苦守白。洁净孤高。有似乎处士之操。含章通理。其馨外达。有似乎儒者之行。排寒拨雪。宣春气于大冬而为百花魁。则有似乎大人之化。挽世道而回至治也。故君子取焉。沧江公之画。而岂徒然哉。噫。沧江公以清操至行。为一代名儒。其德有足以并乎梅者。而守道山樊。隐而不出。其功化不能大被于世。今李公位冢宰参国政。则沧江公之所未能者。而李公有其责矣。夫画小艺也。为其沧江公之遗也。而犹之宝焉。况其重于画者乎。其于梅。必将有取焉。而又能推而大之。则其所就当何如也。余既为沧江公颂其已有。而又以其未焉者。属之李公异日者俟其成终。而以贺夫梅德之全焉。则画之为赞。庸讵不有少迟焉者乎。李公笑曰。余非梅也。将恶乎拨雪。将恶乎宣春。且子迂矣。居斯世而为斯言。是犹求生香于画中之梅。恶乎可哉。余亦大笑。遂记其说。为李公赠。
余敬应曰。诺。然尚有少迟焉者耳。夫梅之德有三。其清苦守白。洁净孤高。有似乎处士之操。含章通理。其馨外达。有似乎儒者之行。排寒拨雪。宣春气于大冬而为百花魁。则有似乎大人之化。挽世道而回至治也。故君子取焉。沧江公之画。而岂徒然哉。噫。沧江公以清操至行。为一代名儒。其德有足以并乎梅者。而守道山樊。隐而不出。其功化不能大被于世。今李公位冢宰参国政。则沧江公之所未能者。而李公有其责矣。夫画小艺也。为其沧江公之遗也。而犹之宝焉。况其重于画者乎。其于梅。必将有取焉。而又能推而大之。则其所就当何如也。余既为沧江公颂其已有。而又以其未焉者。属之李公异日者俟其成终。而以贺夫梅德之全焉。则画之为赞。庸讵不有少迟焉者乎。李公笑曰。余非梅也。将恶乎拨雪。将恶乎宣春。且子迂矣。居斯世而为斯言。是犹求生香于画中之梅。恶乎可哉。余亦大笑。遂记其说。为李公赠。丰墅酬唱录跋
余尝学休心之工。废诗久矣。间为晋庵有梅咏酬而不唱。岭谪以还。遂不复作一句诗。今于丰墅酬唱录篇。止于三者。犹之多也。噫。诗出于心。出而不已。则心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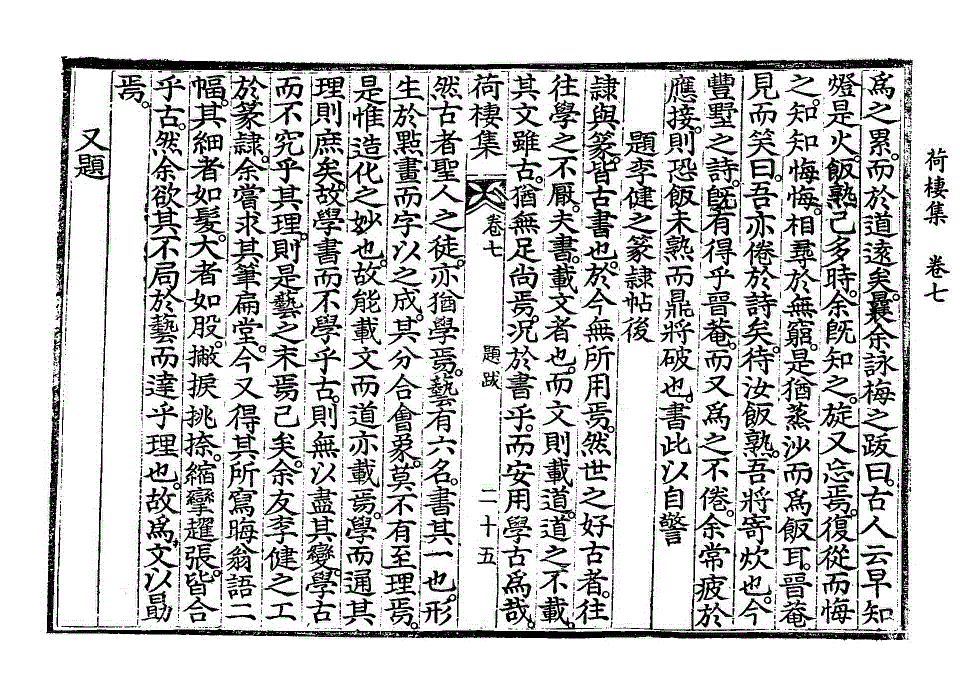 为之累。而于道远矣。曩余咏梅之跋曰。古人云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余既知之。旋又忘焉。复从而悔之。知知悔悔。相寻于无穷。是犹蒸沙而为饭耳。晋庵见而笑曰。吾亦倦于诗矣。待汝饭熟。吾将寄炊也。今丰墅之诗。既有得乎晋庵。而又为之不倦。余常疲于应接。则恐饭未熟而鼎将破也。书此以自警。
为之累。而于道远矣。曩余咏梅之跋曰。古人云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余既知之。旋又忘焉。复从而悔之。知知悔悔。相寻于无穷。是犹蒸沙而为饭耳。晋庵见而笑曰。吾亦倦于诗矣。待汝饭熟。吾将寄炊也。今丰墅之诗。既有得乎晋庵。而又为之不倦。余常疲于应接。则恐饭未熟而鼎将破也。书此以自警。题李健之篆隶帖后
隶与篆。皆古书也。于今无所用焉。然世之好古者。往往学之不厌。夫书。载文者也。而文则载道。道之不载。其文虽古。犹无足尚焉。况于书乎。而安用学古为哉。然古者圣人之徒。亦犹学焉。艺有六名。书其一也。形生于点画而字以之成。其分合会象。莫不有至理焉。是惟造化之妙也。故能载文而道亦载焉。学而通其理则庶矣。故学书而不学乎古。则无以尽其变。学古而不究乎其理。则是艺之末焉已矣。余友李健之工于篆隶。余尝求其笔扁堂。今又得其所写晦翁语二幅。其细者如发。大者如股。撇捩挑捺。缩挛趯张。皆合乎古。然余欲其不局于艺而达乎理也。故为文以勖焉。
题李健之篆隶帖后[又题]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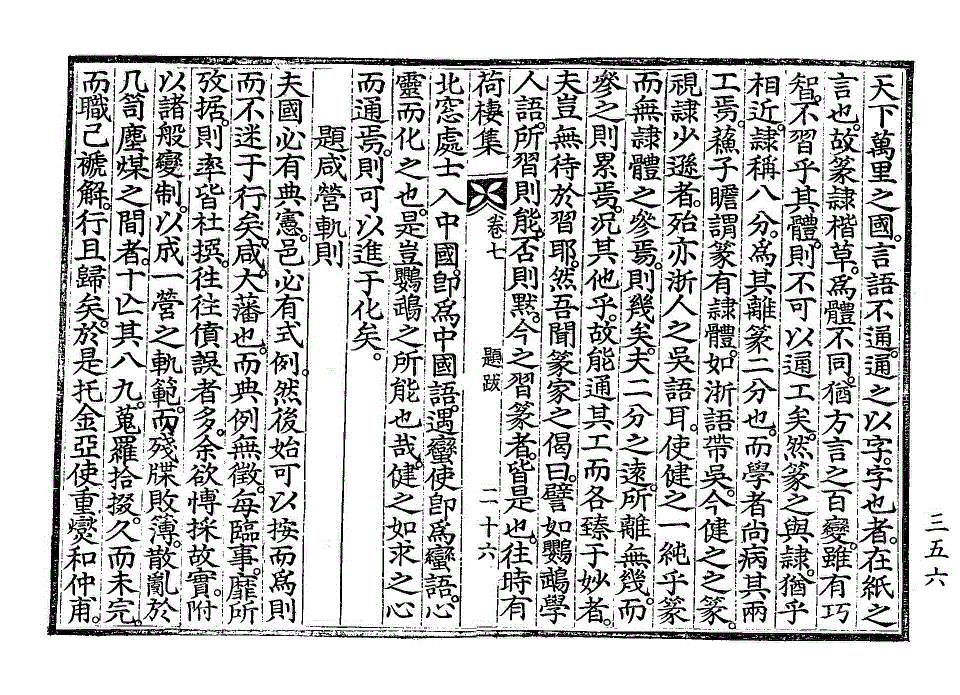 天下万里之国。言语不通。通之以字。字也者。在纸之言也。故篆隶楷草。为体不同。犹方言之百变。虽有巧智。不习乎其体。则不可以通工矣。然篆之与隶。犹乎相近。隶称八分。为其离篆二分也。而学者尚病其两工焉。苏子瞻谓篆有隶体。如浙语带吴。今健之之篆。视隶少逊者。殆亦浙人之吴语耳。使健之一纯乎篆而无隶体之参焉。则几矣。夫二分之远。所离无几。而参之则累焉。况其他乎。故能通其工而各臻于妙者。夫岂无待于习耶。然吾闻篆家之偈曰。譬如鹦鹉学人语。所习则能。否则默。今之习篆者。皆是也。往时有北窗处士入中国。即为中国语。遇蛮使即为蛮语。心灵而化之也。是岂鹦鹉之所能也哉。健之如求之心而通焉。则可以进于化矣。
天下万里之国。言语不通。通之以字。字也者。在纸之言也。故篆隶楷草。为体不同。犹方言之百变。虽有巧智。不习乎其体。则不可以通工矣。然篆之与隶。犹乎相近。隶称八分。为其离篆二分也。而学者尚病其两工焉。苏子瞻谓篆有隶体。如浙语带吴。今健之之篆。视隶少逊者。殆亦浙人之吴语耳。使健之一纯乎篆而无隶体之参焉。则几矣。夫二分之远。所离无几。而参之则累焉。况其他乎。故能通其工而各臻于妙者。夫岂无待于习耶。然吾闻篆家之偈曰。譬如鹦鹉学人语。所习则能。否则默。今之习篆者。皆是也。往时有北窗处士入中国。即为中国语。遇蛮使即为蛮语。心灵而化之也。是岂鹦鹉之所能也哉。健之如求之心而通焉。则可以进于化矣。题咸营轨则
夫国必有典宪。邑必有式例。然后始可以按而为则而不迷于行矣。咸。大藩也。而典例无徵。每临事。靡所考据。则率皆杜撰。往往偾误者多。余欲博采故实。附以诸般变制。以成一营之轨范。而残牒败簿。散乱于几笥尘煤之间者。十亡其八九。蒐罗拾掇。久而未完。而职已褫解。行且归矣。于是托金亚使重燮和仲甫。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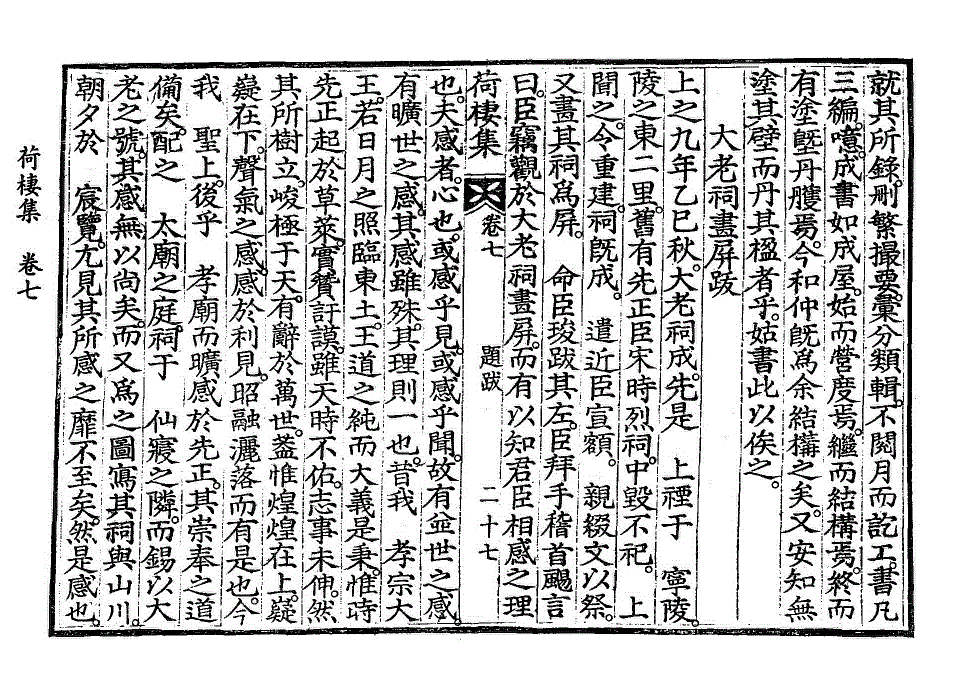 就其所录。删繁撮要。汇分类辑。不阅月而讫工。书凡三编。噫。成书如成屋。始而营度焉。继而结构焉。终而有涂塈丹雘焉。今和仲既为余结构之矣。又安知无涂其壁而丹其楹者乎。姑书此以俟之。
就其所录。删繁撮要。汇分类辑。不阅月而讫工。书凡三编。噫。成书如成屋。始而营度焉。继而结构焉。终而有涂塈丹雘焉。今和仲既为余结构之矣。又安知无涂其壁而丹其楹者乎。姑书此以俟之。大老祠画屏跋
上之九年乙巳秋。大老祠成。先是 上禋于 宁陵。陵之东二里。旧有先正臣宋时烈祠。中毁不祀。 上闻之。令重建。祠既成。 遣近臣宣额。 亲缀文以祭。又画其祠为屏。 命臣㻐跋其左。臣拜手稽首飏言曰。臣窃观于大老祠画屏。而有以知君臣相感之理也。夫感者。心也。或感乎见。或感乎闻。故有并世之感。有旷世之感。其感虽殊。其理则一也。昔我 孝宗大王。若日月之照临东土。王道之纯而大义是秉。惟时先正起于草莱。实赞吁谟。虽天时不佑。志事未伸。然其所树立。峻极于天。有辞于万世。盖惟煌煌在上。嶷嶷在下。声气之感。感于利见。昭融洒落而有是也。今我 圣上。后乎 孝庙而旷感于先正。其崇奉之道备矣。配之 太庙之庭。祠于 仙寝之邻。而锡以大老之号。其感无以尚矣。而又为之图写其祠与山川。朝夕于 宸览。尤见其所感之靡不至矣。然是感也。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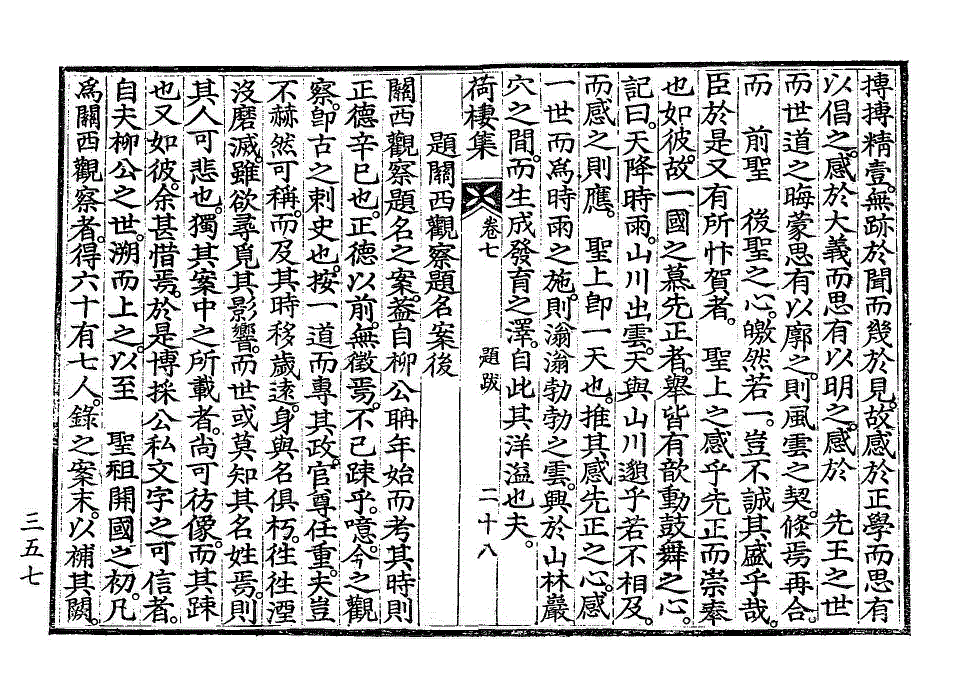 抟抟精壹。无迹于闻而几于见。故感于正学而思有以倡之。感于大义而思有以明之。感于 先王之世而世道之晦蒙思有以廓之。则风云之契。倏焉再合。而 前圣 后圣之心。皦然若一。岂不诚其盛乎哉。臣于是又有所忭贺者。 圣上之感乎先正而崇奉也如彼。故一国之慕先正者。举皆有歆动鼓舞之心。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天与山川邈乎若不相及。而感之则应。 圣上即一天也。推其感先正之心。感一世而为时雨之施。则滃滃勃勃之云。兴于山林岩穴之间。而生成发育之泽。自此其洋溢也夫。
抟抟精壹。无迹于闻而几于见。故感于正学而思有以倡之。感于大义而思有以明之。感于 先王之世而世道之晦蒙思有以廓之。则风云之契。倏焉再合。而 前圣 后圣之心。皦然若一。岂不诚其盛乎哉。臣于是又有所忭贺者。 圣上之感乎先正而崇奉也如彼。故一国之慕先正者。举皆有歆动鼓舞之心。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天与山川邈乎若不相及。而感之则应。 圣上即一天也。推其感先正之心。感一世而为时雨之施。则滃滃勃勃之云。兴于山林岩穴之间。而生成发育之泽。自此其洋溢也夫。题关西观察题名案后
关西观察题名之案。盖自柳公聃年始而考其时则正德辛巳也。正德以前。无徵焉。不已疏乎。噫。今之观察。即古之刺史也。按一道而专其政。官尊任重。夫岂不赫然可称。而及其时移岁远。身与名俱朽。往往湮没磨灭。虽欲寻觅其影响。而世或莫知其名姓焉。则其人可悲也。独其案中之所载者。尚可彷像。而其疏也又如彼。余甚惜焉。于是博采公私文字之可信者。自夫柳公之世。溯而上之。以至 圣祖开国之初。凡为关西观察者。得六十有七人。录之案末。以补其阙。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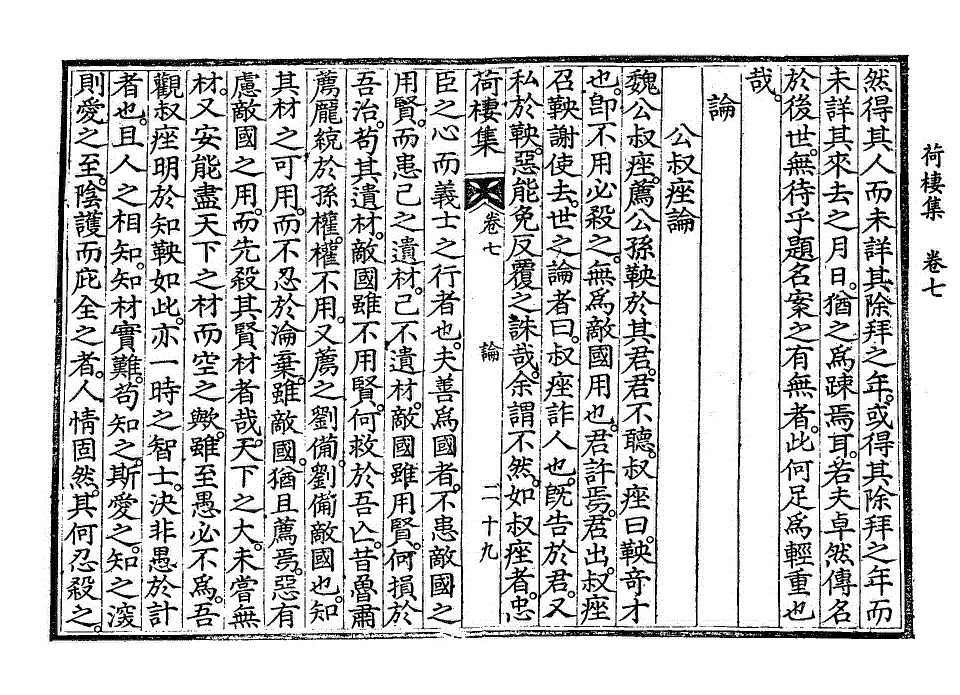 然得其人而未详其除拜之年。或得其除拜之年而未详其来去之月日。犹之为疏焉耳。若夫卓然传名于后世。无待乎题名案之有无者。此何足为轻重也哉。
然得其人而未详其除拜之年。或得其除拜之年而未详其来去之月日。犹之为疏焉耳。若夫卓然传名于后世。无待乎题名案之有无者。此何足为轻重也哉。荷栖集卷之七
论
公叔痤论
魏公叔痤。荐公孙鞅于其君。君不听。叔痤曰。鞅奇才也。即不用必杀之。无为敌国用也。君许焉。君出。叔痤召鞅谢使去。世之论者曰。叔痤诈人也。既告于君。又私于鞅。恶能免反覆之诛哉。余谓不然。如叔痤者。忠臣之心而义士之行者也。夫善为国者。不患敌国之用贤。而患己之遗材。己不遗材。敌国虽用贤。何损于吾治。苟其遗材。敌国虽不用贤。何救于吾亡。昔鲁肃荐庞统于孙权。权不用。又荐之刘备。刘备敌国也。知其材之可用。而不忍于沦弃。虽敌国。犹且荐焉。恶有虑敌国之用。而先杀其贤材者哉。天下之大。未尝无材。又安能尽天下之材而空之欤。虽至愚必不为。吾观叔痤明于知鞅如此。亦一时之智士。决非愚于计者也。且人之相知。知材实难。苟知之。斯爱之。知之深则爱之至。阴护而庇全之者。人情固然。其何忍杀之。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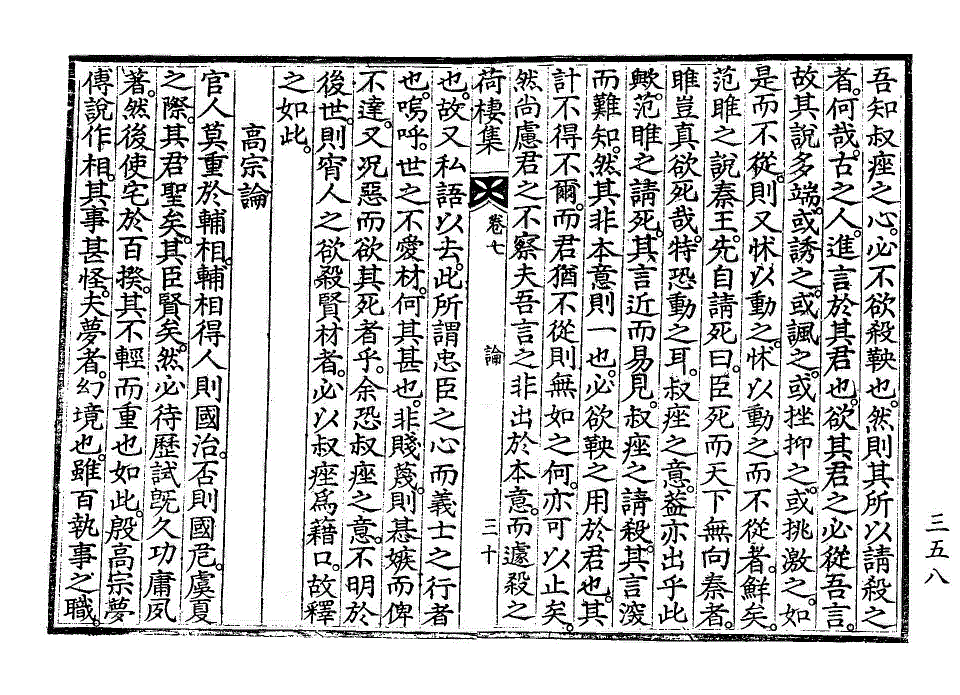 吾知叔痤之心。必不欲杀鞅也。然则其所以请杀之者。何哉。古之人。进言于其君也。欲其君之必从吾言。故其说多端。或诱之。或讽之。或挫抑之。或挑激之。如是而不从。则又怵以动之。怵以动之而不从者。鲜矣。范雎之说秦王。先自请死曰。臣死而天下无向秦者。雎岂真欲死哉。特恐动之耳。叔痤之意。盖亦出乎此欤。范雎之请死。其言近而易见。叔痤之请杀。其言深而难知。然其非本意则一也。必欲鞅之用于君也。其计不得不尔。而君犹不从则无如之何。亦可以止矣。然尚虑君之不察夫吾言之非出于本意。而遽杀之也。故又私语以去。此所谓忠臣之心而义士之行者也。呜呼。世之不爱材。何其甚也。非贱蔑。则惎嫉而俾不达。又况恶而欲其死者乎。余恐叔痤之意。不明于后世。则宵人之欲杀贤材者。必以叔痤为藉口。故释之如此。
吾知叔痤之心。必不欲杀鞅也。然则其所以请杀之者。何哉。古之人。进言于其君也。欲其君之必从吾言。故其说多端。或诱之。或讽之。或挫抑之。或挑激之。如是而不从。则又怵以动之。怵以动之而不从者。鲜矣。范雎之说秦王。先自请死曰。臣死而天下无向秦者。雎岂真欲死哉。特恐动之耳。叔痤之意。盖亦出乎此欤。范雎之请死。其言近而易见。叔痤之请杀。其言深而难知。然其非本意则一也。必欲鞅之用于君也。其计不得不尔。而君犹不从则无如之何。亦可以止矣。然尚虑君之不察夫吾言之非出于本意。而遽杀之也。故又私语以去。此所谓忠臣之心而义士之行者也。呜呼。世之不爱材。何其甚也。非贱蔑。则惎嫉而俾不达。又况恶而欲其死者乎。余恐叔痤之意。不明于后世。则宵人之欲杀贤材者。必以叔痤为藉口。故释之如此。高宗论
官人莫重于辅相。辅相得人则国治。否则国危。虞夏之际。其君圣矣。其臣贤矣。然必待历试既久功庸夙著。然后使宅于百揆。其不轻而重也如此。殷高宗梦傅说作相。其事甚怪。夫梦者。幻境也。虽百执事之职。
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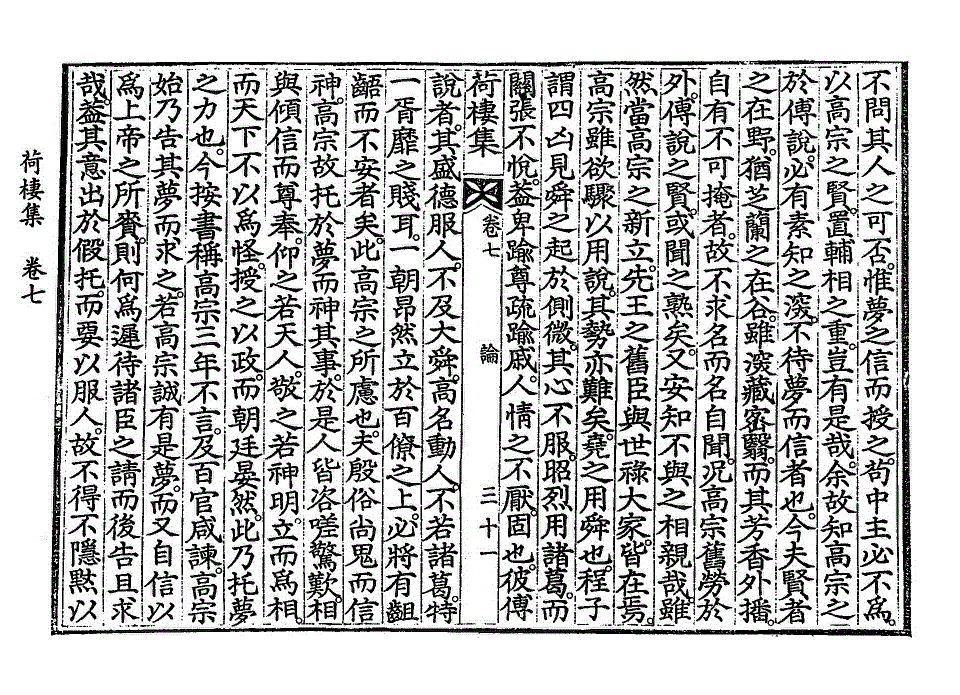 不问其人之可否。惟梦之信而授之。苟中主必不为。以高宗之贤。置辅相之重。岂有是哉。余故知高宗之于傅说。必有素知之深。不待梦而信者也。今夫贤者之在野。犹芝兰之在谷。虽深藏密翳。而其芳香外播。自有不可掩者。故不求名而名自闻。况高宗旧劳于外。傅说之贤。或闻之熟矣。又安知不与之相亲哉。虽然当高宗之新立。先王之旧臣与世禄大家。皆在焉。高宗虽欲骤以用说。其势亦难矣。尧之用舜也。程子谓四凶见舜之起于侧微。其心不服。昭烈用诸葛。而关,张不悦。盖卑踰尊疏踰戚。人情之不厌。固也。彼傅说者。其盛德服人。不及大舜。高名动人。不若诸葛。特一胥靡之贱耳。一朝昂然立于百僚之上。必将有龃龉而不安者矣。此高宗之所虑也。夫殷俗尚鬼而信神。高宗故托于梦而神其事。于是人皆咨嗟惊叹。相与倾信而尊奉。仰之若天人。敬之若神明。立而为相。而天下不以为怪。授之以政。而朝廷晏然。此乃托梦之力也。今按书称高宗三年不言。及百官咸谏。高宗始乃告其梦而求之。若高宗诚有是梦。而又自信以为上帝之所赉。则何为迟待诸臣之请而后告且求哉。盖其意出于假托。而要以服人。故不得不隐默以
不问其人之可否。惟梦之信而授之。苟中主必不为。以高宗之贤。置辅相之重。岂有是哉。余故知高宗之于傅说。必有素知之深。不待梦而信者也。今夫贤者之在野。犹芝兰之在谷。虽深藏密翳。而其芳香外播。自有不可掩者。故不求名而名自闻。况高宗旧劳于外。傅说之贤。或闻之熟矣。又安知不与之相亲哉。虽然当高宗之新立。先王之旧臣与世禄大家。皆在焉。高宗虽欲骤以用说。其势亦难矣。尧之用舜也。程子谓四凶见舜之起于侧微。其心不服。昭烈用诸葛。而关,张不悦。盖卑踰尊疏踰戚。人情之不厌。固也。彼傅说者。其盛德服人。不及大舜。高名动人。不若诸葛。特一胥靡之贱耳。一朝昂然立于百僚之上。必将有龃龉而不安者矣。此高宗之所虑也。夫殷俗尚鬼而信神。高宗故托于梦而神其事。于是人皆咨嗟惊叹。相与倾信而尊奉。仰之若天人。敬之若神明。立而为相。而天下不以为怪。授之以政。而朝廷晏然。此乃托梦之力也。今按书称高宗三年不言。及百官咸谏。高宗始乃告其梦而求之。若高宗诚有是梦。而又自信以为上帝之所赉。则何为迟待诸臣之请而后告且求哉。盖其意出于假托。而要以服人。故不得不隐默以荷栖集卷之七 第 3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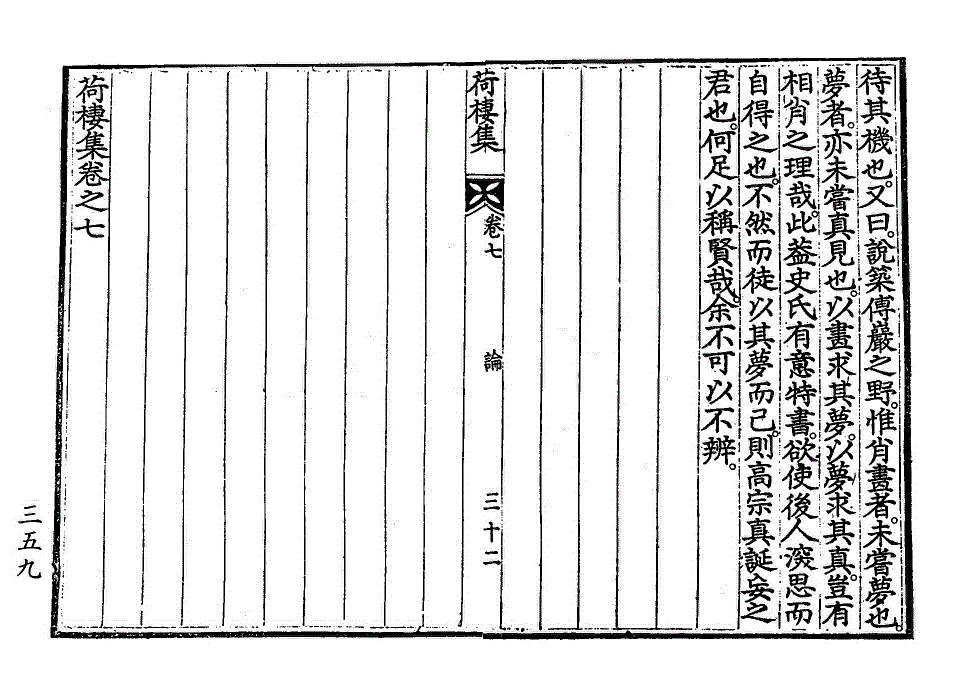 待其机也。又曰。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画者。未尝梦也。梦者。亦未尝真见也。以画求其梦。以梦求其真。岂有相肖之理哉。此盖史氏有意特书。欲使后人深思而自得之也。不然而徒以其梦而已。则高宗真诞妄之君也。何足以称贤哉。余不可以不辨。
待其机也。又曰。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画者。未尝梦也。梦者。亦未尝真见也。以画求其梦。以梦求其真。岂有相肖之理哉。此盖史氏有意特书。欲使后人深思而自得之也。不然而徒以其梦而已。则高宗真诞妄之君也。何足以称贤哉。余不可以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