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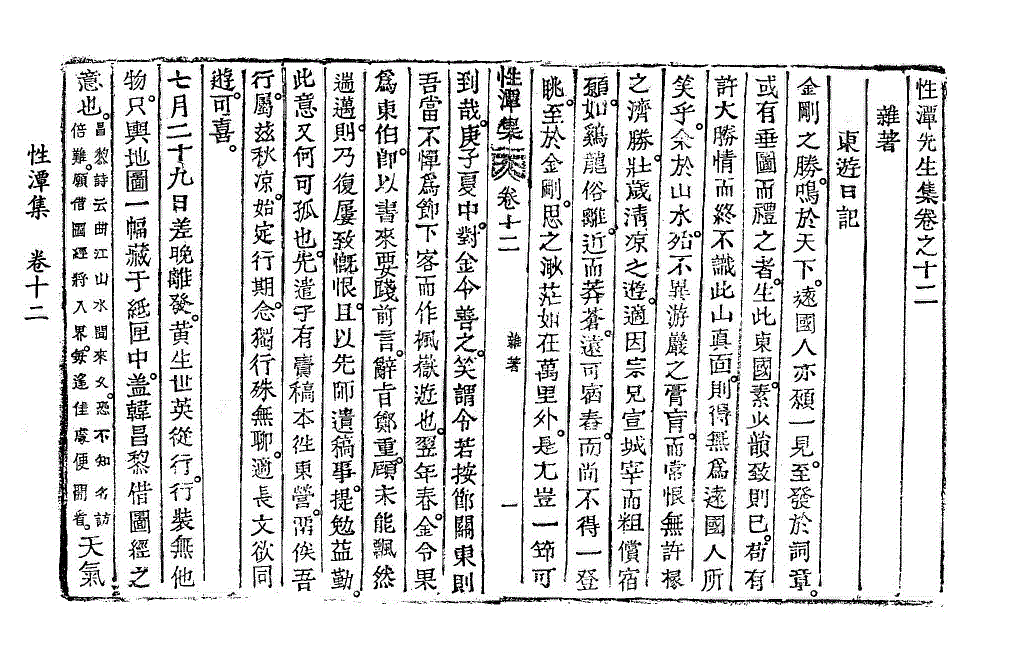 东游日记
东游日记金刚之胜。鸣于天下。远国人亦愿一见。至发于词章。或有垂图而礼之者。生此东国。素少韵致则已。苟有许大胜情而终不识此山真面。则得无为远国人所笑乎。余于山水。殆不异游岩之膏肓。而常恨无许椽之济胜。壮岁清凉之游。适因宗兄宣城宰而粗偿宿愿。如鸡龙俗离。近而莽苍。远可宿舂。而尚不得一登眺。至于金刚。思之渺茫如在万里外。是尤岂一筇可到哉。庚子夏中。对金令善之。笑谓令若按节关东则吾当不惮为节下客而作枫岳游也。翌年春。金令果为东伯。即以书来要践前言。辞旨郑重。顾未能飘然遄迈。则乃复屡致慨恨。且以先师遗稿事。提勉益勤。此意又何可孤也。先遣子有赍稿本往东营。留俟吾行。属玆秋凉。始定行期。念独行殊无聊。适长文欲同游。可喜。
七月二十九日差晚离发。黄生世英从行。行装无他物。只舆地图一幅藏于纸匣中。盖韩昌黎借图经之意也。(昌黎诗云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天气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7L 页
 清朗。野色寥廓。出洞数里。过已觉意想超然。入紫云。与长文同行。薄曛抵文山。
清朗。野色寥廓。出洞数里。过已觉意想超然。入紫云。与长文同行。薄曛抵文山。三十日蚤发。秣马西原邑店。行至十里。长文分路由飞鸿。约以相遇于骊江。夕到凤岩拜姨母。夜听蔡松禾姨叔历说其前春东游时胜趣。恍若此身已在海山间也。
八月初一日辛未旸。早起出门。见岩枫涧菊。秋意将阑。益催人佳兴也。姨叔出示其东游酬唱。而以为古来游枫岳者。鲜不有录。而如农岩所记尽好。后此而欲以芜拙之辞。摹出胜槩则诚难矣。吾先人亦有海山录录甚详。余何用赘焉。故只为此数百句古诗。略记其历览次第。其他诸篇则为同游所唱。自不免强作耳。君之今行。必有奚囊之富。归过时可使得览耶。余笑曰不惟浅见亦如长者所论。素不閒于吟咏记述。虽欲强为。何可得也。海山录是凤岩与南塘,屏溪东游时所录。而颇多好说话。不但记游览之胜而已。为行中披玩。借赍之。临发访郑友德焕,蔡友奎燮。行到镇川邑下。日已亭午。秣马旅店。薄暮入法旺村。外党诸族相访叙话。
初二日朝阴晚雨。食后即发。中路遇雨。着油衣行数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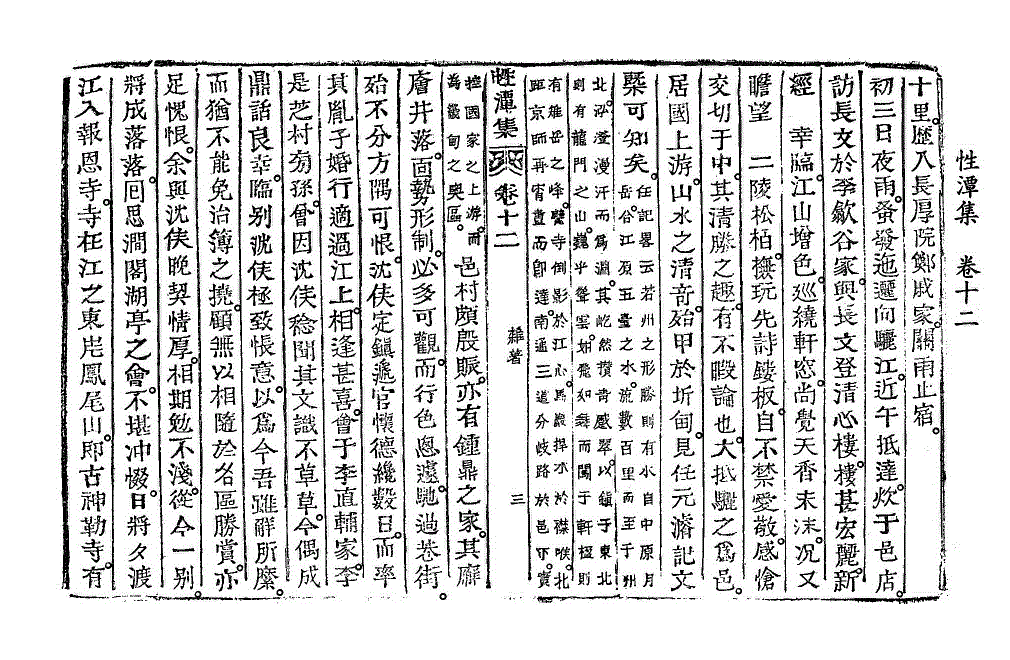 十里。历入长厚院郑戚家。关雨止宿。
十里。历入长厚院郑戚家。关雨止宿。初三日夜雨。蚤发迤逦向骊江。近午抵达。炊于邑店。访长文于李歙谷家。与长文登清心楼。楼甚宏丽。新经 幸临。江山增色。巡绕轩窗。尚觉天香未沫。况又瞻望 二陵松柏。抚玩先诗镂板。自不禁爱敬。感怆交切于中。其清胜之趣。有不暇论也。大抵骊之为邑。居国上游。山水之清奇。殆甲于圻甸。见任元浚记文槩可知矣。(任记略云若州之形胜则有水自中原月岳。合江原五台之水。流数百里而至于州北。泓澄漫汗而为渊。其屹然攒青蹙翠。以镇于东北则有龙门之山。巍乎耸云。如飞如舞而闯于轩楹则有雉岳之峰。甓寺倒影于江心。马岩捍水于襟喉。北距京师再宵昼而即达。南通三道分岐路于邑下。实控国家之上游。而为畿甸之奥区。)邑村颇殷赈。亦有钟鼎之家。其廨廥井落。面势形制。必多可观。而行色悤遽。驰过巷街。殆不分方隅可恨。沈侯定镇递官怀德才数日。而率其胤子婚行适过江上。相逢甚喜。会于李直辅家。李是芝村旁孙。曾因沈侯稔闻其文识不草草。今偶成鼎话良幸。临别沈侯极致怅意。以为今吾虽解所縻。而犹不能免治簿之挠。顾无以相随于名区胜赏。亦足愧恨。余与沈侯晚契情厚。相期勉不浅。从今一别。将成落落。回思涧阁湖亭之会。不堪冲惙。日将夕渡江入报恩寺。寺在江之东岸凤尾山。即古神勒寺。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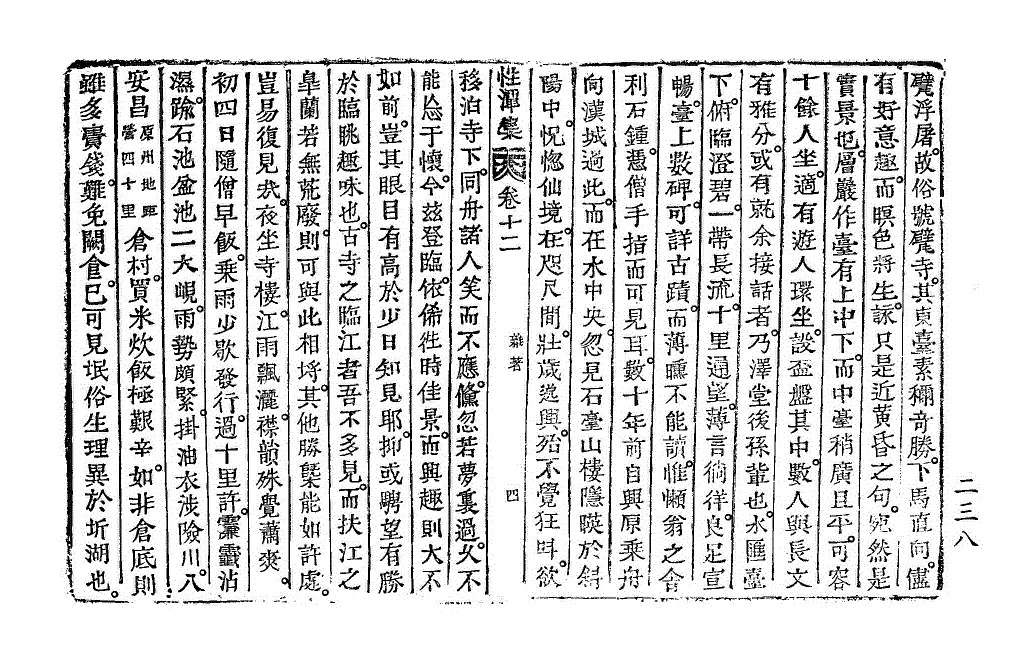 甓浮屠。故俗号甓寺。其东台素称奇胜。下马直向。尽有好意趣。而暝色将生。咏只是近黄昏之句。宛然是实景也。层岩作台有上中下。而中台稍广且平。可容十馀人坐。适有游人环坐。设杯盘其中。数人与长文有雅分。或有就余接话者。乃泽堂后孙辈也。水汇台下。俯临澄碧。一带长流。十里通望。薄言徜徉。良足宣畅。台上数碑。可详古迹。而薄曛不能读。惟懒翁之舍利石钟。凭僧手指而可见耳。数十年前自兴原乘舟向汉城过此。而在水中央。忽见石台山楼隐映于斜阳中。恍惚仙境。在咫尺间。壮岁逸兴。殆不觉狂叫。欲移泊寺下。同舟诸人笑而不应。倏忽若梦里过。久不能忘于怀。今玆登临。依俙往时佳景。而兴趣则大不如前。岂其眼目有高于少日知见耶。抑或骋望有胜于临眺趣味也。古寺之临江者吾不多见。而扶江之皋兰若无荒废。则可与此相埒。其他胜槩能如许处。岂易复见哉。夜坐寺楼。江雨飘洒。襟韵殊觉萧爽。
甓浮屠。故俗号甓寺。其东台素称奇胜。下马直向。尽有好意趣。而暝色将生。咏只是近黄昏之句。宛然是实景也。层岩作台有上中下。而中台稍广且平。可容十馀人坐。适有游人环坐。设杯盘其中。数人与长文有雅分。或有就余接话者。乃泽堂后孙辈也。水汇台下。俯临澄碧。一带长流。十里通望。薄言徜徉。良足宣畅。台上数碑。可详古迹。而薄曛不能读。惟懒翁之舍利石钟。凭僧手指而可见耳。数十年前自兴原乘舟向汉城过此。而在水中央。忽见石台山楼隐映于斜阳中。恍惚仙境。在咫尺间。壮岁逸兴。殆不觉狂叫。欲移泊寺下。同舟诸人笑而不应。倏忽若梦里过。久不能忘于怀。今玆登临。依俙往时佳景。而兴趣则大不如前。岂其眼目有高于少日知见耶。抑或骋望有胜于临眺趣味也。古寺之临江者吾不多见。而扶江之皋兰若无荒废。则可与此相埒。其他胜槩能如许处。岂易复见哉。夜坐寺楼。江雨飘洒。襟韵殊觉萧爽。初四日随僧早饭。乘雨少歇发行。过十里许。𩄡𩆧沾湿。踰石池盆池二大岘。雨势颇紧。挂油衣涉险川。入安昌(原州地距营四十里)仓村。买米炊饭极艰辛。如非仓底则虽多赍钱。难免阙食。已可见氓俗生理异于圻湖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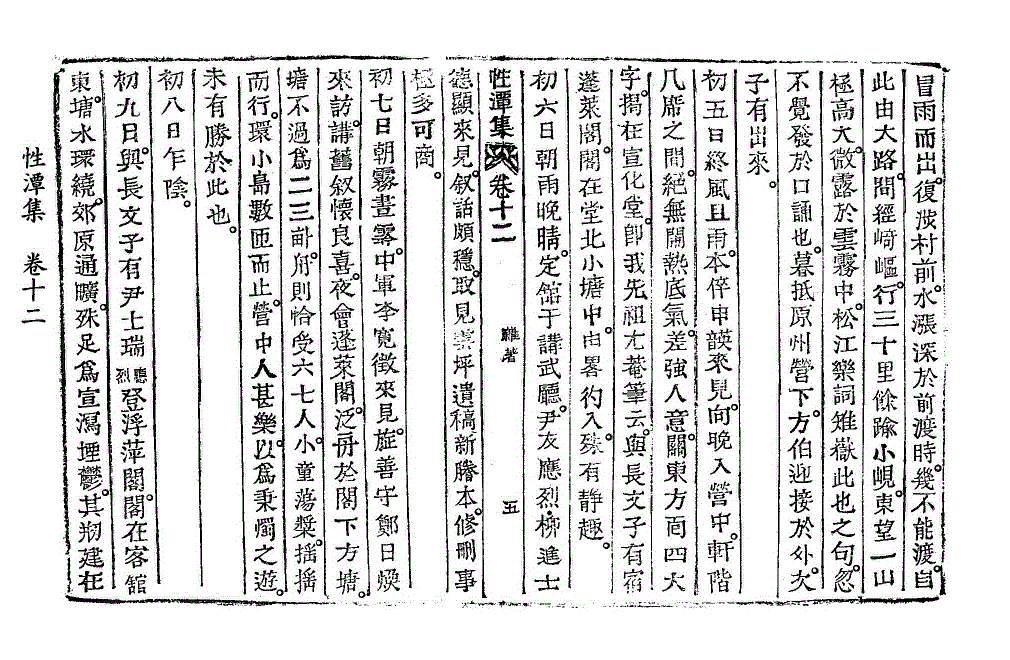 冒雨而出。复涉村前。水涨深于前渡时。几不能渡。自此由大路。间经崎岖。行三十里馀踰小岘。东望一山极高大。微露于云雾中。松江乐词雉岳此也之句。忽不觉发于口诵也。暮抵原州营下。方伯迎接于外。次子有出来。
冒雨而出。复涉村前。水涨深于前渡时。几不能渡。自此由大路。间经崎岖。行三十里馀踰小岘。东望一山极高大。微露于云雾中。松江乐词雉岳此也之句。忽不觉发于口诵也。暮抵原州营下。方伯迎接于外。次子有出来。初五日终风且雨。本倅申韺来见。向晚入营中。轩阶几席之间。绝无闹热底气。差强人意。关东方面四大字。揭在宣化堂。即我先祖尤庵笔云。与长文子有宿蓬莱阁。阁在堂北小塘中。由略彴入。殊有静趣。
初六日朝雨晚晴。定馆于讲武厅。尹友应烈,柳进士德显来见。叙话颇稳。取见云坪遗稿新誊本。修删事极多可商。
初七日朝雾昼𩃬。中军李宽徵来见。㫌善守郑日焕来访。讲旧叙怀良喜。夜会蓬莱阁。泛舟于阁下方塘。塘不过为二三亩。舟则恰受六七人。小童荡桨。摇摇而行。环小岛数匝而止。营中人甚乐。以为秉烛之游。未有胜于此也。
初八日乍阴。
初九日。与长文子有尹士瑞(应烈)登浮萍阁。阁在客馆东。塘水环绕。郊原通旷。殊足为宣泻堙郁。其刱建在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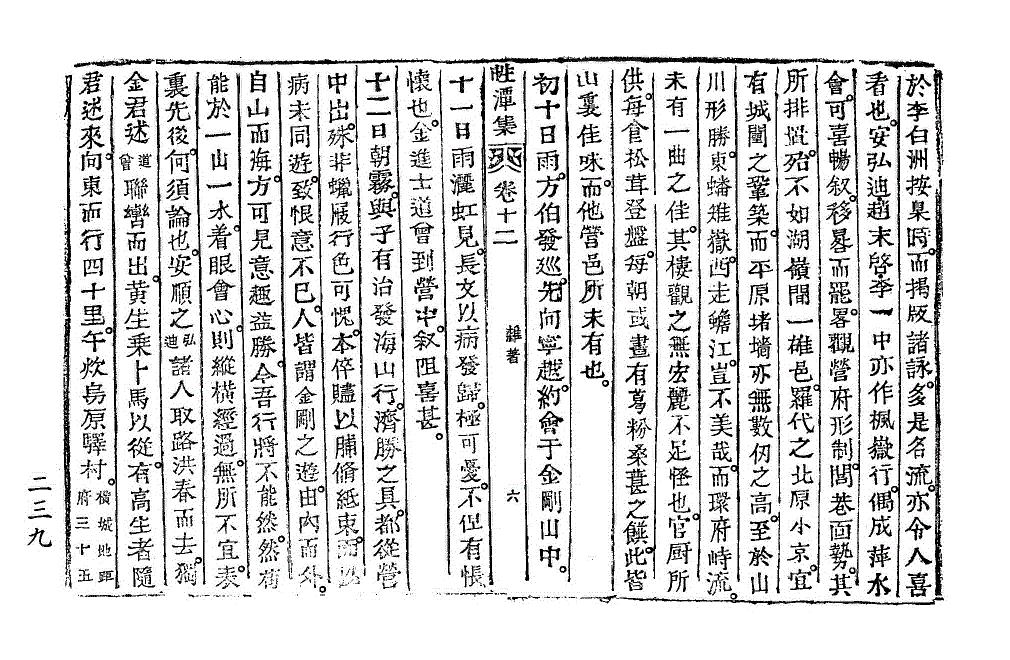 于李白洲按臬时。而揭版诸咏。多是名流。亦令人喜看也。安弘迪,赵末启,李一中亦作枫岳行。偶成萍水会。可喜畅叙。移晷而罢。略观营府形制。闾巷面势。其所排置。殆不如湖岭间一雄邑。罗代之北原小京。宜有城闉之巩筑。而平原堵墙亦无数仞之高。至于山川形胜。东蟠雉岳。西走蟾江。岂不美哉。而环府峙流。未有一曲之佳。其楼观之无宏丽不足怪也。官厨所供。每食松茸登盘。每朝或昼有葛粉桑葚之馔。此皆山里佳味。而他营邑所未有也。
于李白洲按臬时。而揭版诸咏。多是名流。亦令人喜看也。安弘迪,赵末启,李一中亦作枫岳行。偶成萍水会。可喜畅叙。移晷而罢。略观营府形制。闾巷面势。其所排置。殆不如湖岭间一雄邑。罗代之北原小京。宜有城闉之巩筑。而平原堵墙亦无数仞之高。至于山川形胜。东蟠雉岳。西走蟾江。岂不美哉。而环府峙流。未有一曲之佳。其楼观之无宏丽不足怪也。官厨所供。每食松茸登盘。每朝或昼有葛粉桑葚之馔。此皆山里佳味。而他营邑所未有也。初十日雨。方伯发巡。先向宁越。约会于金刚山中。
十一日雨洒虹见。长文以病发归。极可忧。不但有怅怀也。金进士道曾到营中。叙阻喜甚。
十二日朝雾。与子有治发海山行。济胜之具。都从营中出。殊非蜡屐行色可愧。本倅赆以脯脩纸束。而以病未同游。致恨意不已。人皆谓金刚之游。由内而外。自山而海。方可见意趣益胜。今吾行将不能然。然苟能于一山一水。着眼会心。则纵横经过。无所不宜。表里先后。何须论也。安顺之(弘迪)诸人取路洪春而去。独金君述(道曾)联辔而出。黄生乘卜马以从。有高生者随君述来。向东而行四十里。午炊乌原驿村。(横城地。距府三十五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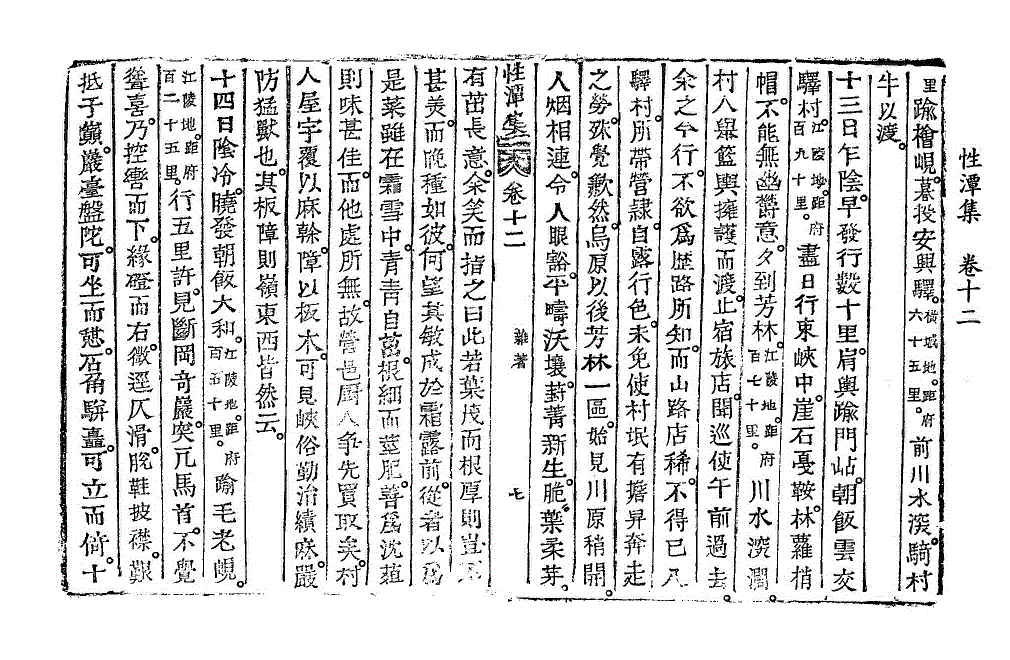 里。)踰桧岘。暮投安兴驿。(横城地。距府六十五里。)前川水深。骑村牛以渡。
里。)踰桧岘。暮投安兴驿。(横城地。距府六十五里。)前川水深。骑村牛以渡。十三日乍阴。早发行数十里。肩舆踰门岾。朝饭云交驿村。(江陵地。距府百九十里。)尽日行束峡中。崖石戛鞍。林萝梢帽。不能无幽郁意。夕到芳林。(江陵地。距府百七十里。)川水深阔。村人举篮舆拥护而渡。止宿旅店。闻巡使午前过去。余之今行。不欲为历路所知。而山路店稀。不得已入驿村。所带营隶。自露行色。未免使村氓有担舁奔走之劳。殊觉歉然。乌原以后芳林一区。始见川原稍开。人烟相连。令人眼豁。平畴沃壤。葑菁新生。脆叶柔芽。有茁长意。余笑而指之曰此若叶茂而根厚则岂不甚美。而晚种如彼。何望其敏成于霜露前。从者以为是菜虽在霜雪中。青青自茁。根细而茎肥。善为沈菹则味甚佳。而他处所无。故营邑厨人争先买取矣。村人屋宇覆以麻干。障以板木。可见峡俗勤治绩麻。严防猛兽也。其板障则岭东西皆然云。
十四日阴冷。晓发朝饭大和。(江陵地。距府百五十里。)踰毛老岘。(江陵地。距府百二十五里。)行五里许。见断冈奇岩。突兀马首。不觉耸喜。乃控辔而下。缘磴而右。微径仄滑。脱鞋披襟。艰抵于巅。岩台盘陀。可坐而憩。石角骈矗。可立而倚。十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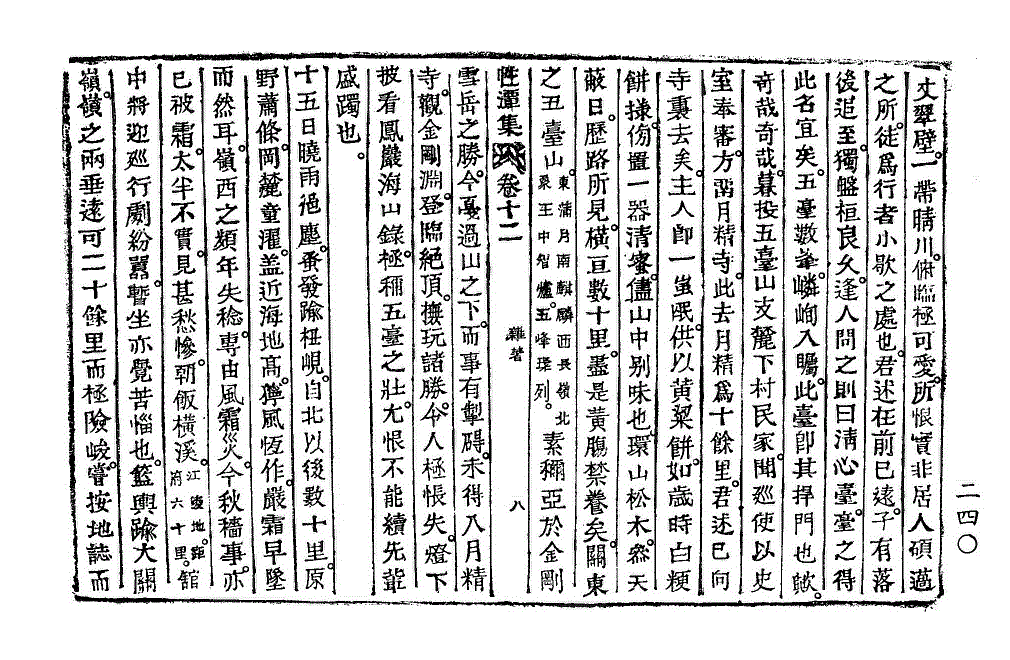 丈翠壁。一带晴川。俯临极可爱。所恨实非居人硕薖之所。徒为行者小歇之处也。君述在前已远。子有落后追至。独盘桓良久。逢人问之则曰清心台。台之得此名宜矣。五台数峰。嶙峋入瞩。此台即其捍门也欤。奇哉奇哉。暮投五台山支麓下村民家。闻巡使以史室奉审。方留月精寺。此去月精为十馀里。君述已向寺里去矣。主人即一蚩氓。供以黄粱饼。如岁时白粳饼㨾。傍置一器清蜜。尽山中别味也。环山松木。参天蔽日。历路所见。横亘数十里。尽是黄肠禁养矣。关东之丑台山。(东蒲月南麒麟西长岭北象王中智炉。五峰环列。)素称亚于金刚雪岳之胜。今戛过山之下。而事有掣碍。未得入月精寺。观金刚渊。登临绝顶。抚玩诸胜。令人极怅失。灯下披看凤岩海山录。极称五台之壮。尤恨不能续先辈盛躅也。
丈翠壁。一带晴川。俯临极可爱。所恨实非居人硕薖之所。徒为行者小歇之处也。君述在前已远。子有落后追至。独盘桓良久。逢人问之则曰清心台。台之得此名宜矣。五台数峰。嶙峋入瞩。此台即其捍门也欤。奇哉奇哉。暮投五台山支麓下村民家。闻巡使以史室奉审。方留月精寺。此去月精为十馀里。君述已向寺里去矣。主人即一蚩氓。供以黄粱饼。如岁时白粳饼㨾。傍置一器清蜜。尽山中别味也。环山松木。参天蔽日。历路所见。横亘数十里。尽是黄肠禁养矣。关东之丑台山。(东蒲月南麒麟西长岭北象王中智炉。五峰环列。)素称亚于金刚雪岳之胜。今戛过山之下。而事有掣碍。未得入月精寺。观金刚渊。登临绝顶。抚玩诸胜。令人极怅失。灯下披看凤岩海山录。极称五台之壮。尤恨不能续先辈盛躅也。十五日晓雨浥尘。蚤发踰杻岘。自北以后数十里。原野萧条。冈麓童濯。盖近海地高。狞风恒作。严霜早坠而然耳。岭西之频年失稔。专由风霜灾。今秋穑事。亦已被霜。太半不实。见甚愁惨。朝饭横溪。(江陵地。距府六十里。)馆中将迎巡行剧纷嚣。暂坐亦觉苦恼也。篮舆踰大关岭。岭之两垂远可二十馀里而极险峻。尝按地志而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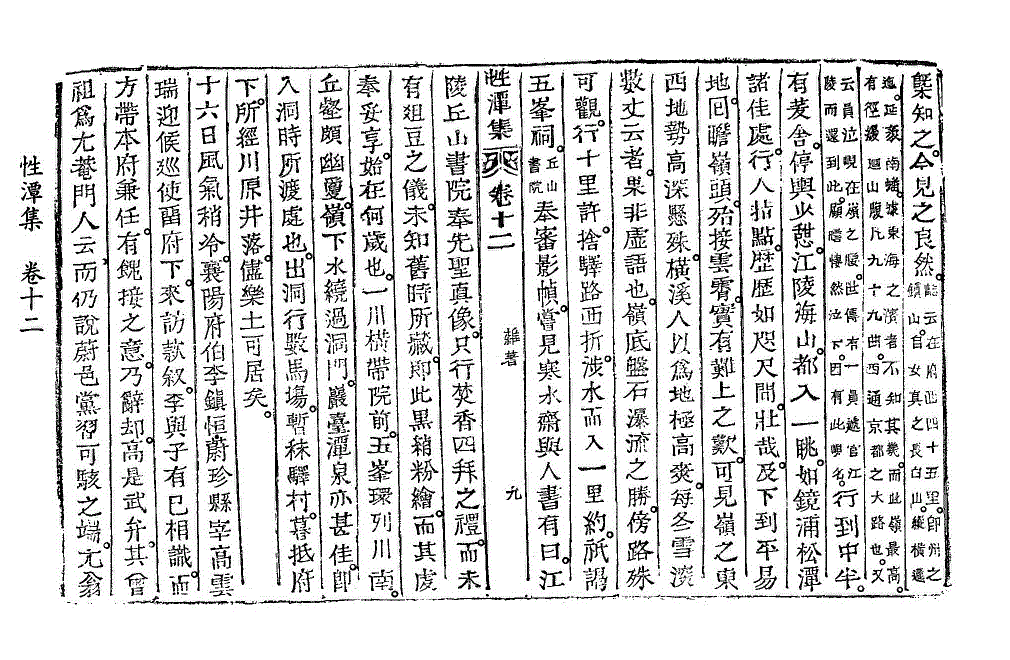 槩知之。今见之良然。(志云在府西四十五里。即州之镇山。自女真之长白山。纵横逦迤。延袤南蟠。据东海之滨者不知其几。而此岭最高。有径缦回山腹凡九十九曲。西通京都之大路也。又云员泣岘在岭之腰。世传有一员递官江陵而还到此。顾瞻悽然泣下。因有此岘名。)行到中半。有茇舍。停舆少憩。江陵海山。都入一眺。如镜浦松潭诸佳处。行人指点。历历如咫尺间。壮哉。及下到平易地。回瞻岭头。殆接云霄。实有难上之叹。可见岭之东西地势高深悬殊。横溪人以为地极高爽。每冬雪深数丈云者。果非虚语也。岭底盘石瀑流之胜。傍路殊可观。行十里许。舍驿路西折。涉水而入一里约。祇谒五峰祠。(丘山书院。)奉审影帧。尝见寒水斋与人书有曰。江陵丘山书院奉先圣真像。只行焚香四拜之礼。而未有俎豆之仪。未知旧时所藏。即此黑绡粉绘。而其虔奉妥享。始在何岁也。一川横带院前。五峰环列川南。丘壑颇幽夐。岭下水绕过洞门。岩台潭泉亦甚佳。即入洞时所渡处也。出洞行数马场。暂秣驿村。暮抵府下。所经川原井落。尽乐土可居矣。
槩知之。今见之良然。(志云在府西四十五里。即州之镇山。自女真之长白山。纵横逦迤。延袤南蟠。据东海之滨者不知其几。而此岭最高。有径缦回山腹凡九十九曲。西通京都之大路也。又云员泣岘在岭之腰。世传有一员递官江陵而还到此。顾瞻悽然泣下。因有此岘名。)行到中半。有茇舍。停舆少憩。江陵海山。都入一眺。如镜浦松潭诸佳处。行人指点。历历如咫尺间。壮哉。及下到平易地。回瞻岭头。殆接云霄。实有难上之叹。可见岭之东西地势高深悬殊。横溪人以为地极高爽。每冬雪深数丈云者。果非虚语也。岭底盘石瀑流之胜。傍路殊可观。行十里许。舍驿路西折。涉水而入一里约。祇谒五峰祠。(丘山书院。)奉审影帧。尝见寒水斋与人书有曰。江陵丘山书院奉先圣真像。只行焚香四拜之礼。而未有俎豆之仪。未知旧时所藏。即此黑绡粉绘。而其虔奉妥享。始在何岁也。一川横带院前。五峰环列川南。丘壑颇幽夐。岭下水绕过洞门。岩台潭泉亦甚佳。即入洞时所渡处也。出洞行数马场。暂秣驿村。暮抵府下。所经川原井落。尽乐土可居矣。十六日风气稍冷。襄阳府伯李镇恒,蔚珍县宰高云瑞迎候巡使留府下。来访款叙。李与子有已相识。而方带本府兼任。有馈接之意。乃辞却。高是武弁。其曾祖为尤庵门人云。而仍说蔚邑党习可骇之端。尤翁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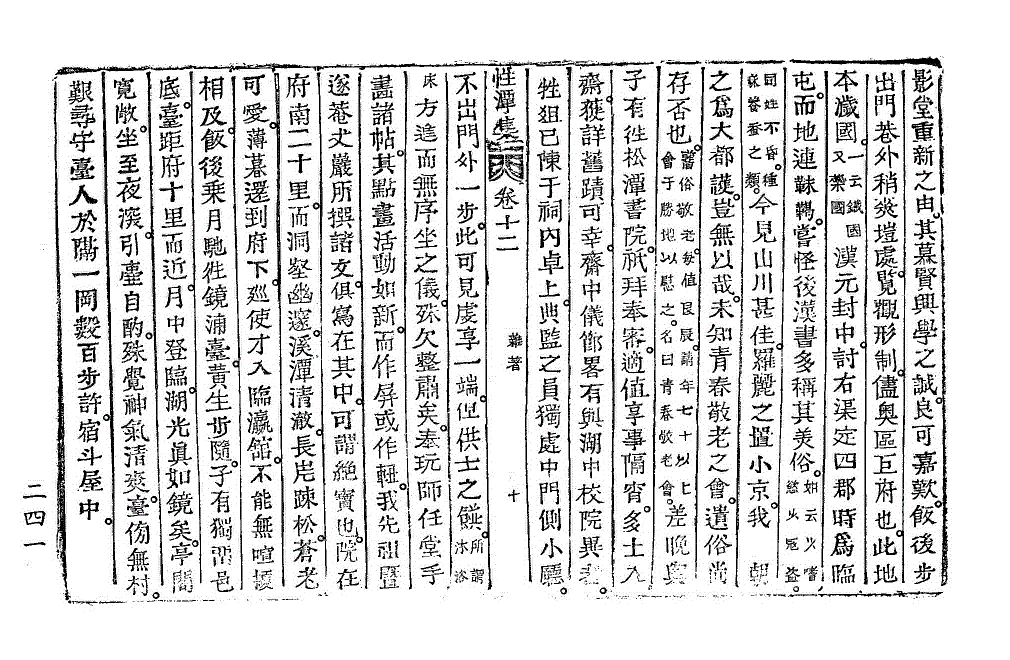 影堂重新之由。其慕贤兴学之诚。良可嘉叹。饭后步出门巷外稍爽垲处。览观形制。尽奥区巨府也。此地本濊国。(一云铁国又蕊国。)汉元封中。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而地连靺鞨。尝怪后汉书多称其美俗。(如云少嗜欲少寇盗。同姓不昏。种麻养蚕之类。)今见山川甚佳。罗丽之置小京。我 朝之为大都护。岂无以哉。未知青春敬老之会。遗俗尚存否也。旧俗敬老。每值艮(一作良)辰。请年七十以上会于胜地以慰之。名曰青春敬老会。 差晚与子有往松潭书院。祇拜奉审。适值享事隔宵。多士入斋。获详旧迹可幸。斋中仪节略有与湖中校院异者。牲俎已陈于祠内卓上。典监之员独处中门侧小厅。不出门外一步。此可见虔享一端。但供士之馔。(所谓沐浴床。)方进而无序坐之仪。殊欠整肃矣。奉玩师任堂手画诸帖。其点画活动如新。而作屏或作轴。我先祖暨遂庵丈岩所撰诸文。俱写在其中。可谓绝宝也。院在府南二十里。而洞壑幽邃。溪潭清澈。长岸疏松。苍老可爱。薄暮还到府下。巡使才入临瀛馆。不能无喧扰相及。饭后乘月驰往镜浦台。黄生步随。子有独留邑底。台距府十里而近。月中登临。湖光真如镜矣。亭阁宽敞。坐至夜深。引壶自酌。殊觉神气清爽。台傍无村。艰寻守台人于隔一冈数百步许。宿斗屋中。
影堂重新之由。其慕贤兴学之诚。良可嘉叹。饭后步出门巷外稍爽垲处。览观形制。尽奥区巨府也。此地本濊国。(一云铁国又蕊国。)汉元封中。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而地连靺鞨。尝怪后汉书多称其美俗。(如云少嗜欲少寇盗。同姓不昏。种麻养蚕之类。)今见山川甚佳。罗丽之置小京。我 朝之为大都护。岂无以哉。未知青春敬老之会。遗俗尚存否也。旧俗敬老。每值艮(一作良)辰。请年七十以上会于胜地以慰之。名曰青春敬老会。 差晚与子有往松潭书院。祇拜奉审。适值享事隔宵。多士入斋。获详旧迹可幸。斋中仪节略有与湖中校院异者。牲俎已陈于祠内卓上。典监之员独处中门侧小厅。不出门外一步。此可见虔享一端。但供士之馔。(所谓沐浴床。)方进而无序坐之仪。殊欠整肃矣。奉玩师任堂手画诸帖。其点画活动如新。而作屏或作轴。我先祖暨遂庵丈岩所撰诸文。俱写在其中。可谓绝宝也。院在府南二十里。而洞壑幽邃。溪潭清澈。长岸疏松。苍老可爱。薄暮还到府下。巡使才入临瀛馆。不能无喧扰相及。饭后乘月驰往镜浦台。黄生步随。子有独留邑底。台距府十里而近。月中登临。湖光真如镜矣。亭阁宽敞。坐至夜深。引壶自酌。殊觉神气清爽。台傍无村。艰寻守台人于隔一冈数百步许。宿斗屋中。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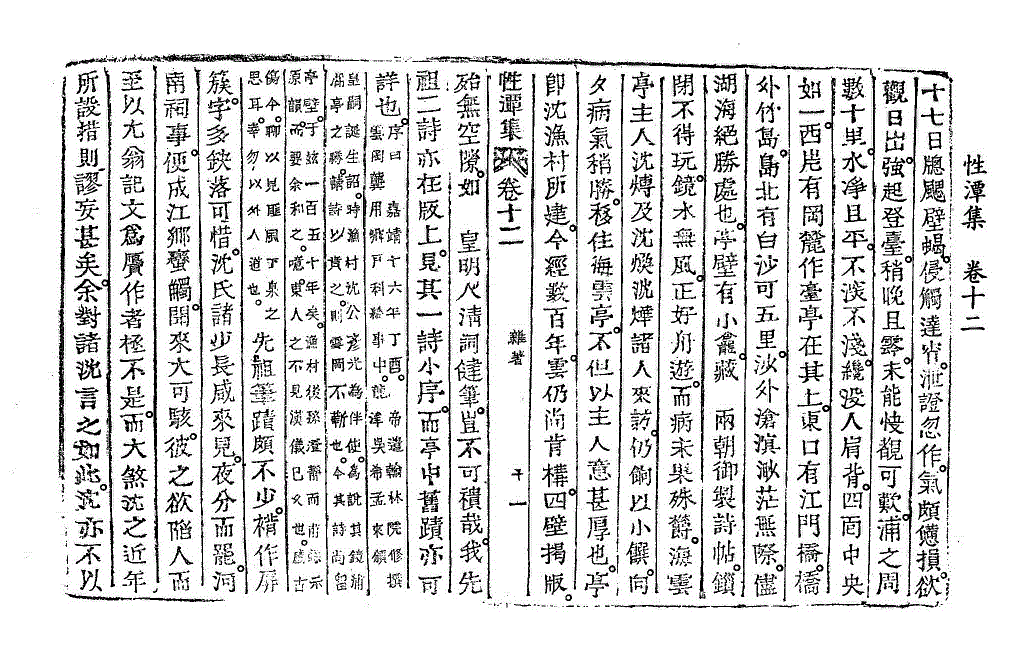 十七日窗飔壁蝎。侵触达宵。泄證忽作。气颇惫损。欲观日出。强起登台。稍晚且𩃬。未能快睹可叹。浦之周数十里。水净且平。不深不浅。才没人肩背。四面中央如一。西岸有冈麓作台亭在其上。东口有江门桥。桥外竹岛。岛北有白沙可五里。沙外沧溟渺茫无际。尽湖海绝胜处也。亭壁有小龛。藏 两朝御制诗帖。锁闭不得玩。镜水无风。正好舟游。而病未果殊郁。海云亭主人沈煿及沈焕,沈烨诸人来访。仍饷以小馔。向夕病气稍胜。移住海云亭。不但以主人意甚厚也。亭即沈渔村所建。今经数百年。云仍尚肯构。四壁揭版。殆无空隙。如 皇明人清词健笔。岂不可䙌哉。我先祖二诗亦在版上。见其一诗小序。而亭中旧迹亦可详也。(序曰 嘉靖十六年丁酉。 帝遣翰林院修撰云冈龚用乡户科给事中。龙津吴希孟来颁 皇嗣诞生诏。时渔村沈公彦光为伴使。为说其镜浦湖亭之胜。请诗以贲之。则云冈不靳也。今其诗尚留亭壁。于玆一百五十年矣。渔村后孙澄静而甫录示原韵。而要余和之。噫。东人之不见汉仪已久也。感古伤今。聊以见匪风下泉之思耳。幸勿以外人道也。)先祖笔迹颇不少。褙作屏簇。字多缺落可惜。沈氏诸少长咸来见。夜分而罢。河南祠事。便成江乡蛮触。闻来大可骇。彼之欲陷人而至以尤翁记文为赝作者极不是。而大煞沈之近年所设措则谬妄甚矣。余对诸沈言之如此。沈亦不以
十七日窗飔壁蝎。侵触达宵。泄證忽作。气颇惫损。欲观日出。强起登台。稍晚且𩃬。未能快睹可叹。浦之周数十里。水净且平。不深不浅。才没人肩背。四面中央如一。西岸有冈麓作台亭在其上。东口有江门桥。桥外竹岛。岛北有白沙可五里。沙外沧溟渺茫无际。尽湖海绝胜处也。亭壁有小龛。藏 两朝御制诗帖。锁闭不得玩。镜水无风。正好舟游。而病未果殊郁。海云亭主人沈煿及沈焕,沈烨诸人来访。仍饷以小馔。向夕病气稍胜。移住海云亭。不但以主人意甚厚也。亭即沈渔村所建。今经数百年。云仍尚肯构。四壁揭版。殆无空隙。如 皇明人清词健笔。岂不可䙌哉。我先祖二诗亦在版上。见其一诗小序。而亭中旧迹亦可详也。(序曰 嘉靖十六年丁酉。 帝遣翰林院修撰云冈龚用乡户科给事中。龙津吴希孟来颁 皇嗣诞生诏。时渔村沈公彦光为伴使。为说其镜浦湖亭之胜。请诗以贲之。则云冈不靳也。今其诗尚留亭壁。于玆一百五十年矣。渔村后孙澄静而甫录示原韵。而要余和之。噫。东人之不见汉仪已久也。感古伤今。聊以见匪风下泉之思耳。幸勿以外人道也。)先祖笔迹颇不少。褙作屏簇。字多缺落可惜。沈氏诸少长咸来见。夜分而罢。河南祠事。便成江乡蛮触。闻来大可骇。彼之欲陷人而至以尤翁记文为赝作者极不是。而大煞沈之近年所设措则谬妄甚矣。余对诸沈言之如此。沈亦不以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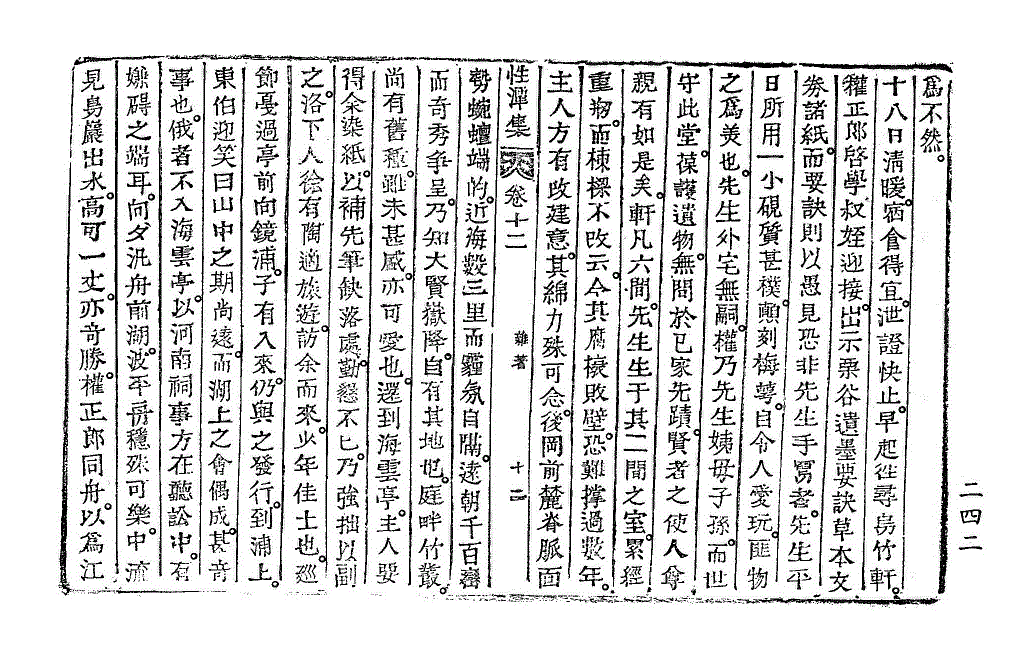 为不然。
为不然。十八日清暖。宿食得宜。泄證快止。早起往寻乌竹轩。权正郎启学叔侄迎接。出示栗谷遗墨要诀草本文券诸纸。而要诀则以愚见恐非先生手写者。先生平日所用一小砚质甚朴。颠刻梅萼。自令人爱玩。匪物之为美也。先生外宅无嗣。权乃先生姨母子孙。而世守此堂。葆护遗物。无间于己家先迹。贤者之使人尊亲有如是矣。轩凡六间。先生生于其二间之室。累经重刱。而栋梁不改云。今其腐榱败壁。恐难撑过数年。主人方有改建意。其绵力殊可念。后冈前麓脊脉面势蜿蟺端的。近海数三里而霾氛自隔。远朝千百峦而奇秀争呈。乃知大贤岳降。自有其地也。庭畔竹丛。尚有旧种。虽未甚盛。亦可爱也。还到海云亭。主人要得余染纸。以补先笔缺落处。勤恳不已。乃强拙以副之。洛下人徐有陶适旅游。访余而来。少年佳士也。巡节戛过亭前向镜浦。子有入来。仍与之发行。到浦上。东伯迎笑曰山中之期尚远。而湖上之会偶成。甚奇事也。俄者不入海云亭。以河南祠事方在听讼中。有嫌碍之端耳。向夕汎舟前湖。波平舟稳殊可乐。中流见鸟岩出水。高可一丈。亦奇胜。权正郎同舟。以为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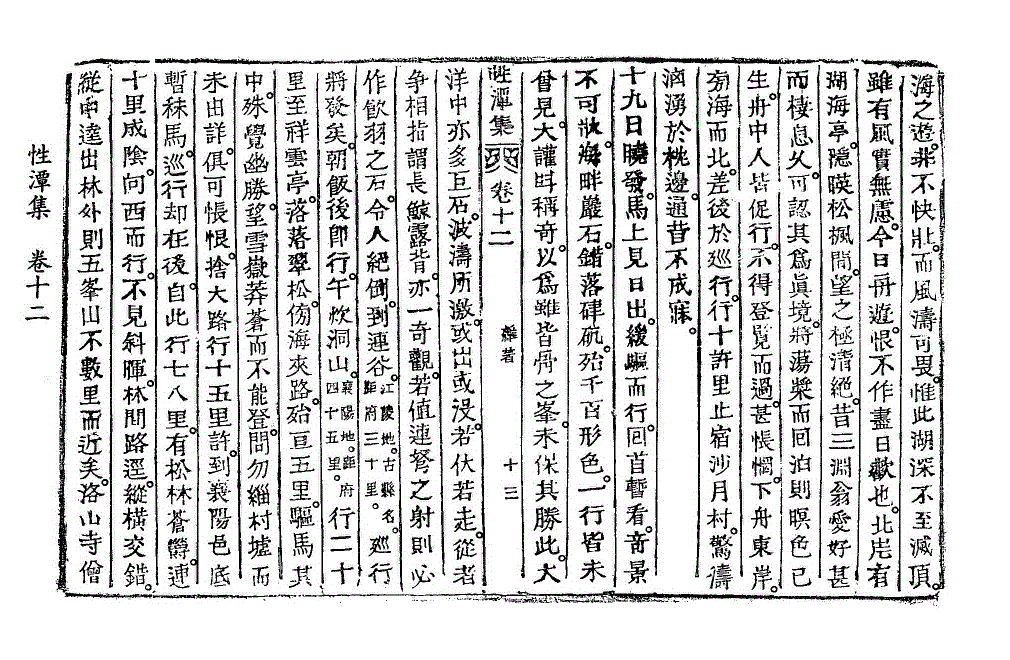 海之游。非不快壮。而风涛可畏。惟此湖深不至灭顶。虽有风实无虑。今日舟游。恨不作尽日欢也。北岸有湖海亭。隐映松枫间。望之极清绝。昔三渊翁爱好甚而栖息久。可认其为真境。将荡桨而回泊则暝色已生。舟中人皆促行。不得登览而过。甚怅惘。下舟东岸。旁海而北。差后于巡行。行十许里止宿沙月村。惊涛汹涌于枕边。通昔不成寐。
海之游。非不快壮。而风涛可畏。惟此湖深不至灭顶。虽有风实无虑。今日舟游。恨不作尽日欢也。北岸有湖海亭。隐映松枫间。望之极清绝。昔三渊翁爱好甚而栖息久。可认其为真境。将荡桨而回泊则暝色已生。舟中人皆促行。不得登览而过。甚怅惘。下舟东岸。旁海而北。差后于巡行。行十许里止宿沙月村。惊涛汹涌于枕边。通昔不成寐。十九日晓发。马上见日出。缓驱而行。回首暂看。奇景不可状。海畔岩石。错落硉矹。殆千百形色。一行皆未曾见。大欢叫称奇。以为虽皆骨之峰。未保其胜此。大洋中亦多巨石。波涛所激。或出或没。若伏若走。从者争相指谓长鲸露背。亦一奇观。若值连弩之射则必作饮羽之石。令人绝倒。到连谷。(江陵地。古县名。距府三十里。)巡行将发矣。朝饭后即行。午炊洞山。(襄阳地。距府四十五里。)行二十里至祥云亭。落落翠松。傍海夹路。殆亘五里。驱马其中。殊觉幽胜。望雪岳莽苍而不能登。问勿缁村墟而未由详。俱可怅恨。舍大路行十五里许。到襄阳邑底暂秣马。巡行却在后。自此行七八里。有松林苍郁。连十里成阴。向西而行。不见斜晖。林间路径。纵横交错。从中逵出林外则五峰山不数里而近矣。洛山寺僧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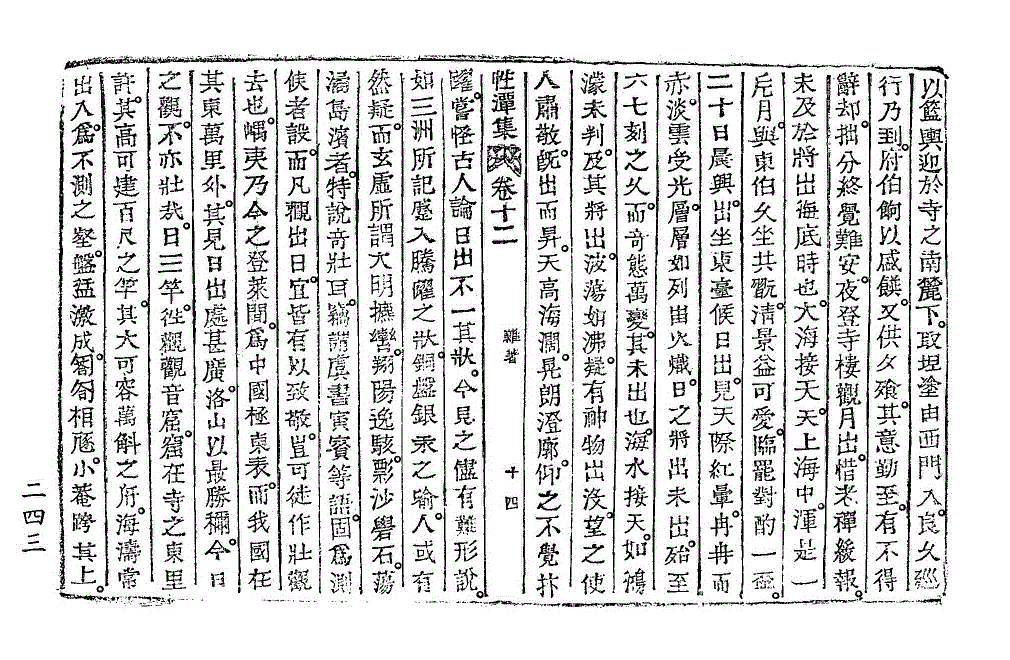 以篮舆迎于寺之南麓下。取坦涂由西门入。良久巡行乃到。府伯饷以盛馔。又供夕飧。其意勤至。有不得辞却。拙分终觉难安。夜登寺楼观月出。惜老禅缓报。未及于将出海底时也。大海接天。天上海中。浑是一片月。与东伯久坐共玩。清景益可爱。临罢对酌一杯。
以篮舆迎于寺之南麓下。取坦涂由西门入。良久巡行乃到。府伯饷以盛馔。又供夕飧。其意勤至。有不得辞却。拙分终觉难安。夜登寺楼观月出。惜老禅缓报。未及于将出海底时也。大海接天。天上海中。浑是一片月。与东伯久坐共玩。清景益可爱。临罢对酌一杯。二十日晨兴。出坐东台候日出。见天际红晕。冉冉而赤。淡云受光。层层如列岫火炽。日之将出未出。殆至六七刻之久。而奇态万变。其未出也。海水接天。如鸿濛未判。及其将出。波荡如沸。疑有神物出没。望之使人肃敬。既出而升。天高海阔。晃朗澄廓。仰之不觉抃跃。尝怪古人论日出不一其状。今见之尽有难形说。如三洲所记蹙入腾跃之状。铜盘银汞之喻。人或有然疑。而玄虚所谓大明㩠辔。翔阳逸骇。彯沙礐石。荡潏岛滨者。特说奇壮耳。窃谓虞书寅宾等语。固为测候者设。而凡观出日。宜皆有以致敬。岂可徒作壮观去也。嵎夷乃今之登莱间。为中国极东表。而我国在其东万里外。其见日出处甚广。洛山以最胜称。今日之观。不亦壮哉。日三竿。往观观音窟。窟在寺之东里许。其高可建百尺之竿。其大可容万斛之舟。海涛常出入。为不测之壑。盘盓激成。匒匌相豗。小庵跨其上。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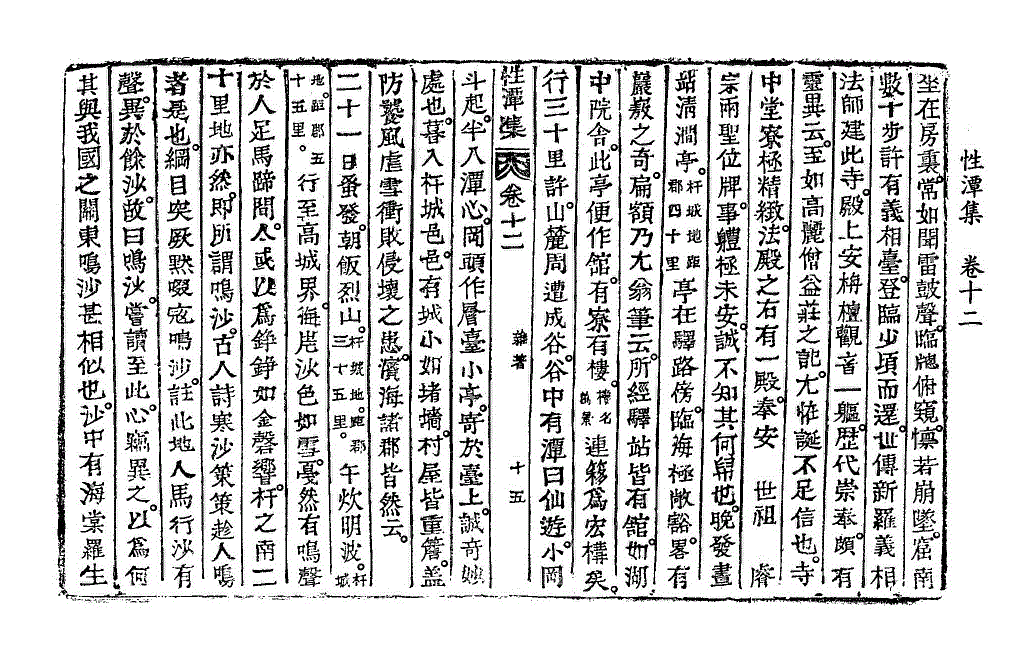 坐在房里。常如闻雷鼓声。临窗俯窥。懔若崩坠。窟南数十步许有义相台。登临少顷而还。世传新罗义相法师建此寺。殿上安栴檀观音一躯。历代崇奉。颇有灵异云。至如高丽僧益庄之记。尤怪诞不足信也。寺中堂寮极精致。法殿之右有一殿。奉安 世祖 睿宗两圣位牌。事体极未安。诚不知其何帠也。晚发昼站清涧亭。(杆城地。距郡四十里。)亭在驿路傍。临海极敞豁。略有岩㟼之奇。扁额乃尤翁笔云。所经驿站皆有馆。如湖中院舍。此亭便作馆。有寮有楼。(楼名万景。)连簃为宏构矣。行三十里许。山麓周遭成谷。谷中有潭曰仙游。小冈斗起。半入潭心。冈头作层台小亭。寄于台上。诚奇妙处也。暮入杆城邑。邑有城小如堵墙。村屋皆重檐。盖防饕风虐雪冲败侵坏之患。滨海诸郡皆然云。
坐在房里。常如闻雷鼓声。临窗俯窥。懔若崩坠。窟南数十步许有义相台。登临少顷而还。世传新罗义相法师建此寺。殿上安栴檀观音一躯。历代崇奉。颇有灵异云。至如高丽僧益庄之记。尤怪诞不足信也。寺中堂寮极精致。法殿之右有一殿。奉安 世祖 睿宗两圣位牌。事体极未安。诚不知其何帠也。晚发昼站清涧亭。(杆城地。距郡四十里。)亭在驿路傍。临海极敞豁。略有岩㟼之奇。扁额乃尤翁笔云。所经驿站皆有馆。如湖中院舍。此亭便作馆。有寮有楼。(楼名万景。)连簃为宏构矣。行三十里许。山麓周遭成谷。谷中有潭曰仙游。小冈斗起。半入潭心。冈头作层台小亭。寄于台上。诚奇妙处也。暮入杆城邑。邑有城小如堵墙。村屋皆重檐。盖防饕风虐雪冲败侵坏之患。滨海诸郡皆然云。二十一日蚤发。朝饭烈山。(杆城地。距郡三十五里。)午炊明波。(杆城地。距郡五十五里。)行至高城界。海岸沙色如雪。戛然有鸣声于人足马蹄间。人或以为铮铮如金磬响。杆之南二十里地亦然。即所谓鸣沙。古人诗寒沙策策趁人鸣者是也。纲目突厥默啜寇鸣沙。注此地人马行沙有声。异于馀沙。故曰鸣沙。尝读至此。心窃异之。以为何其与我国之关东鸣沙甚相似也。沙中有海棠罗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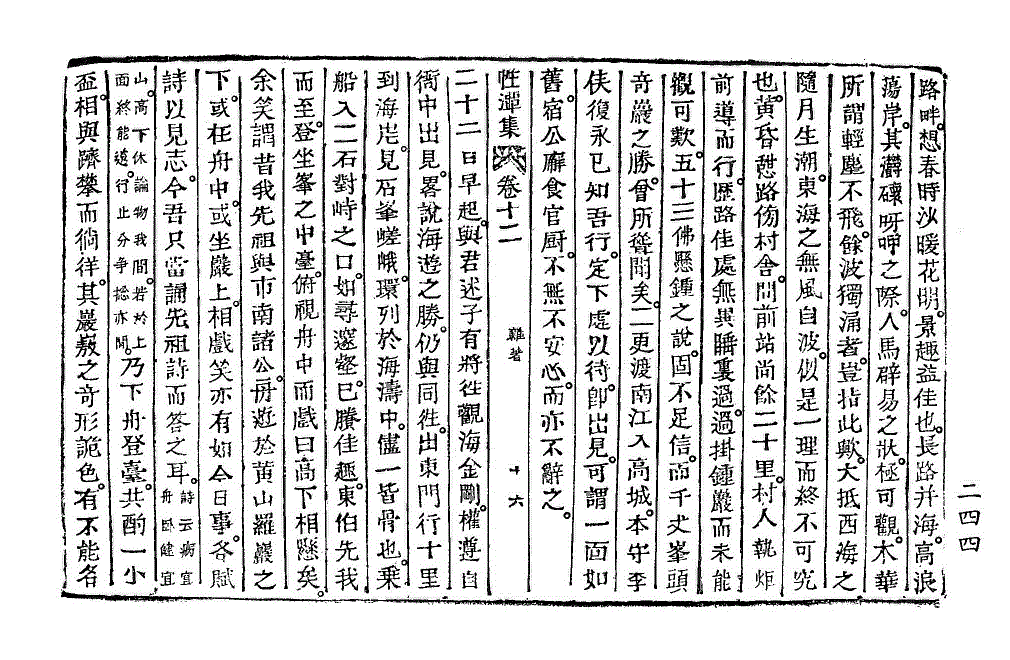 路畔。想春时沙暖花明。景趣益佳也。长路并海。高浪荡岸。其灪䃶呀呷之际。人马辟易之状。极可观。木华所谓轻尘不飞。馀波独涌者。岂指此欤。大抵西海之随月生潮。东海之无风自波。似是一理而终不可究也。黄昏憩路傍村舍。问前站尚馀二十里。村人执炬前导而行。历路佳处无异睡里过。过挂钟岩而未能观可叹。五十三佛悬钟之说。固不足信。而千丈峰头奇岩之胜。曾所耸闻矣。二更渡南江入高城。本守李侯复永已知吾行。定下处以待。即出见。可谓一面如旧。宿公廨食官厨。不无不安心。而亦不辞之。
路畔。想春时沙暖花明。景趣益佳也。长路并海。高浪荡岸。其灪䃶呀呷之际。人马辟易之状。极可观。木华所谓轻尘不飞。馀波独涌者。岂指此欤。大抵西海之随月生潮。东海之无风自波。似是一理而终不可究也。黄昏憩路傍村舍。问前站尚馀二十里。村人执炬前导而行。历路佳处无异睡里过。过挂钟岩而未能观可叹。五十三佛悬钟之说。固不足信。而千丈峰头奇岩之胜。曾所耸闻矣。二更渡南江入高城。本守李侯复永已知吾行。定下处以待。即出见。可谓一面如旧。宿公廨食官厨。不无不安心。而亦不辞之。二十二日早起。与君述子有将往观海金刚。权遵自衙中出见。略说海游之胜。仍与同往。出东门行十里到海岸。见石峰嵯峨。环列于海涛中。尽一皆骨也。乘船入二石对峙之口。如寻邃壑。已剩佳趣。东伯先我而至。登坐峰之中台。俯视舟中而戏曰高下相悬矣。余笑谓昔我先祖与市南诸公。舟游于黄山罗岩之下。或在舟中。或坐岩上。相戏笑亦有如今日事。各赋诗以见志。今吾只当诵先祖诗而答之耳。(诗云病宜舟卧健宜山。高下休论物我间。若于上面终能透。行止分争总亦閒。)乃下舟登台。共酌一小杯。相与跻攀而徜徉。其岩㟼之奇形诡色。有不能名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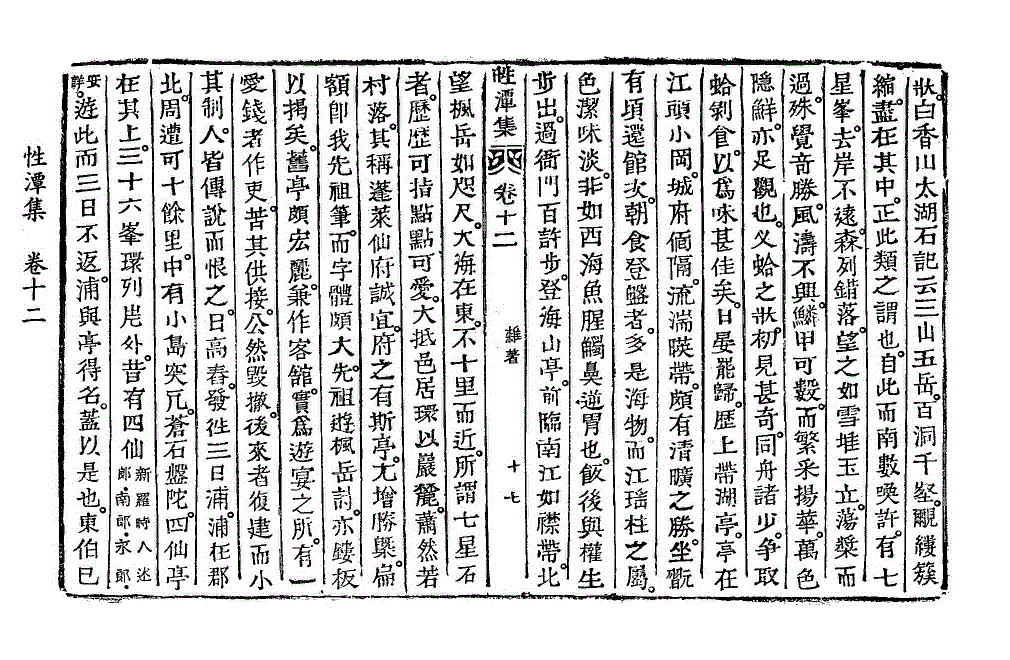 状。白香山太湖石记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正此类之谓也。自此而南数唤许。有七星峰。去岸不远。森列错落。望之如雪堆玉立。荡桨而过。殊觉奇胜。风涛不兴。鳞甲可数。而繁采扬华。万色隐鲜。亦足观也。叉蛤之状。初见甚奇。同舟诸少。争取蛤剥食。以为味甚佳矣。日晏罢归。历上带湖亭。亭在江头小冈。城府偭隔。流湍映带。颇有清旷之胜。坐玩有顷还馆次。朝食登盘者。多是海物。而江瑶柱之属。色洁味淡。非如西海鱼腥触鼻逆胃也。饭后与权生步出。过衙门百许步。登海山亭。前临南江如襟带。北望枫岳如咫尺。大海在东。不十里而近。所谓七星石者。历历可指点点可爱。大抵邑居环以岩麓。萧然若村落。其称蓬莱仙府诚宜。府之有斯亭。尤增胜槩。扁额即我先祖笔。而字体颇大。先祖游枫岳诗。亦镂板以揭矣。旧亭颇宏丽。兼作客馆。实为游宴之所。有一爱钱者作吏。苦其供接。公然毁撤。后来者复建而小其制。人皆传说而恨之。日高舂。发往三日浦。浦在郡北。周遭可十馀里。中有小岛突兀。苍石盘陀。四仙亭在其上。三十六峰环列岸外。昔有四仙(新罗时人述郎,南郎,永郎,安详。)游此而三日不返。浦与亭得名。盖以是也。东伯已
状。白香山太湖石记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正此类之谓也。自此而南数唤许。有七星峰。去岸不远。森列错落。望之如雪堆玉立。荡桨而过。殊觉奇胜。风涛不兴。鳞甲可数。而繁采扬华。万色隐鲜。亦足观也。叉蛤之状。初见甚奇。同舟诸少。争取蛤剥食。以为味甚佳矣。日晏罢归。历上带湖亭。亭在江头小冈。城府偭隔。流湍映带。颇有清旷之胜。坐玩有顷还馆次。朝食登盘者。多是海物。而江瑶柱之属。色洁味淡。非如西海鱼腥触鼻逆胃也。饭后与权生步出。过衙门百许步。登海山亭。前临南江如襟带。北望枫岳如咫尺。大海在东。不十里而近。所谓七星石者。历历可指点点可爱。大抵邑居环以岩麓。萧然若村落。其称蓬莱仙府诚宜。府之有斯亭。尤增胜槩。扁额即我先祖笔。而字体颇大。先祖游枫岳诗。亦镂板以揭矣。旧亭颇宏丽。兼作客馆。实为游宴之所。有一爱钱者作吏。苦其供接。公然毁撤。后来者复建而小其制。人皆传说而恨之。日高舂。发往三日浦。浦在郡北。周遭可十馀里。中有小岛突兀。苍石盘陀。四仙亭在其上。三十六峰环列岸外。昔有四仙(新罗时人述郎,南郎,永郎,安详。)游此而三日不返。浦与亭得名。盖以是也。东伯已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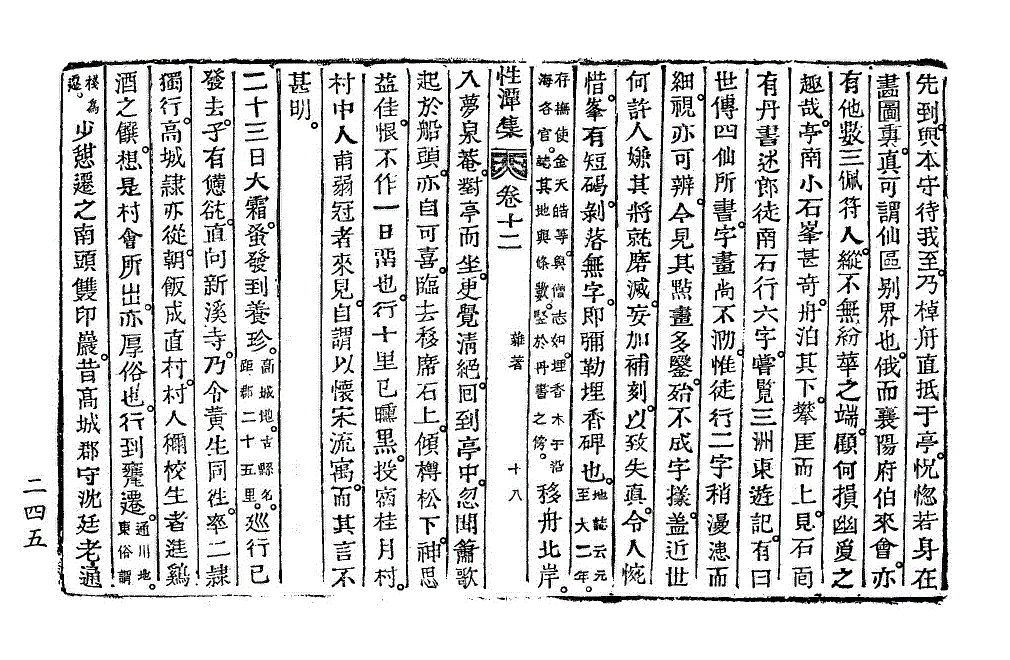 先到。与本守待我至。乃棹舟直抵于亭。恍惚若身在画图里。真可谓仙区别界也。俄而襄阳府伯来会。亦有他数三佩符人。纵不无纷华之端。顾何损幽夐之趣哉。亭南小石峰甚奇。舟泊其下。攀厓而上。见石面有丹书述郎徒南石行六字。尝览三洲东游记。有曰世传四仙所书。字画尚不泐。惟徒行二字稍漫漶而细。视亦可辨。今见其点画多凿。殆不成字㨾。盖近世何许人嫌其将就磨灭。妄加补刻。以致失真。令人惋惜。峰有短碣。剥落无字。即弥勒埋香碑也。(地志云元至大二年。存抚使金天皓等。与僧志如。埋香木于沿海各官。志其地与条数。竖于丹书之傍。)移舟北岸。入梦泉庵。对亭而坐。更觉清绝。回到亭中。忽闻箫歌起于船头。亦自可喜。临去移席石上。倾樽松下。神思益佳。恨不作一日留也。行十里已曛黑。投宿桂月村。村中人甫弱冠者来见。自谓以怀宋流寓。而其言不甚明。
先到。与本守待我至。乃棹舟直抵于亭。恍惚若身在画图里。真可谓仙区别界也。俄而襄阳府伯来会。亦有他数三佩符人。纵不无纷华之端。顾何损幽夐之趣哉。亭南小石峰甚奇。舟泊其下。攀厓而上。见石面有丹书述郎徒南石行六字。尝览三洲东游记。有曰世传四仙所书。字画尚不泐。惟徒行二字稍漫漶而细。视亦可辨。今见其点画多凿。殆不成字㨾。盖近世何许人嫌其将就磨灭。妄加补刻。以致失真。令人惋惜。峰有短碣。剥落无字。即弥勒埋香碑也。(地志云元至大二年。存抚使金天皓等。与僧志如。埋香木于沿海各官。志其地与条数。竖于丹书之傍。)移舟北岸。入梦泉庵。对亭而坐。更觉清绝。回到亭中。忽闻箫歌起于船头。亦自可喜。临去移席石上。倾樽松下。神思益佳。恨不作一日留也。行十里已曛黑。投宿桂月村。村中人甫弱冠者来见。自谓以怀宋流寓。而其言不甚明。二十三日大霜。蚤发到养珍。(高城地。古县名。距郡二十五里。)巡行已发去。子有惫㞃。直向新溪寺。乃令黄生同往。率二隶独行。高城隶亦从。朝饭成直村。村人称校生者进鸡酒之馔。想是村会所出。亦厚俗也。行到瓮迁。(通川地。东俗谓栈为迁。)少憩迁之南头双印岩。昔高城郡守沈廷老,通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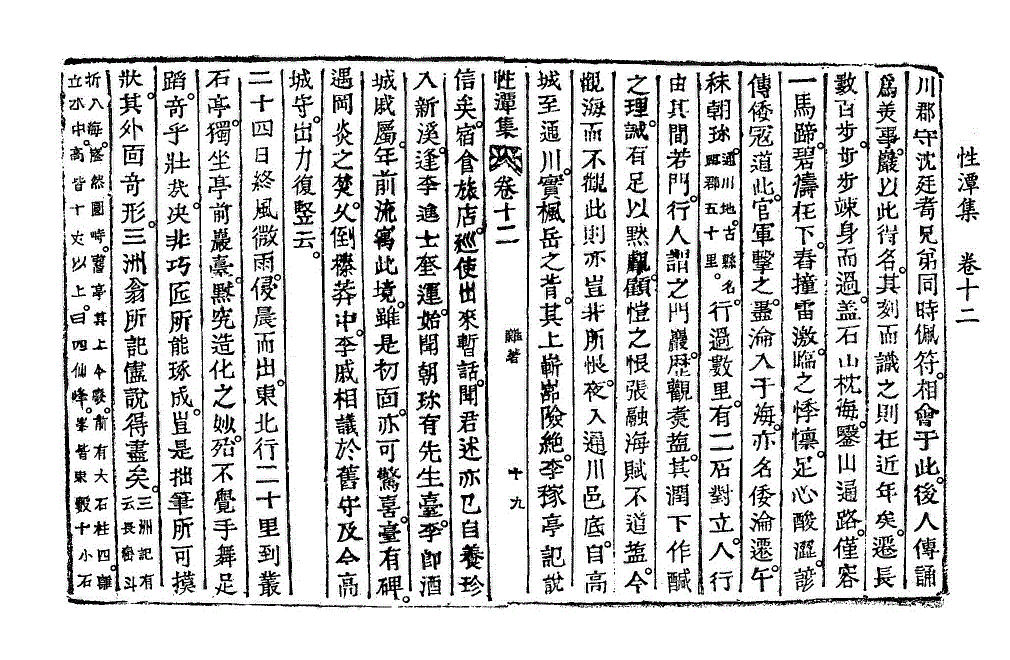 川郡守沈廷耇兄弟同时佩符。相会于此。后人传诵为美事。岩以此得名。其刻而识之则在近年矣。迁长数百步。步步竦身而过。盖石山枕海。凿山通路。仅容一马蹄。碧涛在下。舂撞雷激。临之悸懔。足心酸涩。谚传倭寇道此。官军击之。尽沦入于海。亦名倭沦迁。午秣朝珍。(通川地。古县名。距郡五十里。)行过数里。有二石对立。人行由其间若门。行人谓之门岩。历观煮盐。其润下作咸之理。诚有足以默觑。顾恺之恨张融海赋不道盐。今观海而不观此则亦岂非所恨。夜入通川邑底。自高城至通川。实枫岳之背。其上崭嵓险绝。李稼亭记说信矣。宿食旅店。巡使出来暂话。闻君述亦已自养珍入新溪。逢李进士奎运。始闻朝珍有先生台。李即酒城戚属。年前流寓此境。虽是初面。亦可惊喜。台有碑。遇冈炎之焚。久倒榛莽中。李戚相议于旧守及今高城守。出力复竖云。
川郡守沈廷耇兄弟同时佩符。相会于此。后人传诵为美事。岩以此得名。其刻而识之则在近年矣。迁长数百步。步步竦身而过。盖石山枕海。凿山通路。仅容一马蹄。碧涛在下。舂撞雷激。临之悸懔。足心酸涩。谚传倭寇道此。官军击之。尽沦入于海。亦名倭沦迁。午秣朝珍。(通川地。古县名。距郡五十里。)行过数里。有二石对立。人行由其间若门。行人谓之门岩。历观煮盐。其润下作咸之理。诚有足以默觑。顾恺之恨张融海赋不道盐。今观海而不观此则亦岂非所恨。夜入通川邑底。自高城至通川。实枫岳之背。其上崭嵓险绝。李稼亭记说信矣。宿食旅店。巡使出来暂话。闻君述亦已自养珍入新溪。逢李进士奎运。始闻朝珍有先生台。李即酒城戚属。年前流寓此境。虽是初面。亦可惊喜。台有碑。遇冈炎之焚。久倒榛莽中。李戚相议于旧守及今高城守。出力复竖云。二十四日终风微雨。侵晨而出。东北行二十里到丛石亭。独坐亭前岩台。默究造化之妙。殆不觉手舞足蹈。奇乎壮哉。决非巧匠所能琢成。岂是拙笔所可摸状。其外面奇形。三洲翁所记尽说得尽矣。(三洲记有云长峦斗折入海。隆然圆峙。旧亭其上今废。前有大石柱四。离立水中。高皆十丈以上。曰四仙峰。峰皆束数十小石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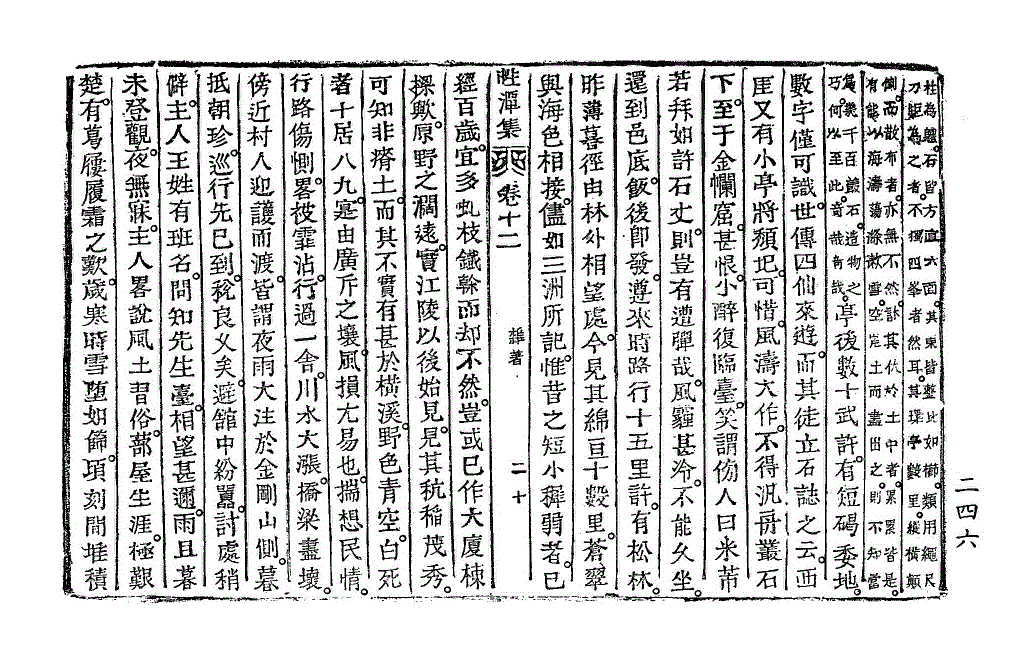 柱为体。石皆方直六面。其束皆整比如栉。类用绳尺刀钜为之者。不独四峰者然耳。其环亭数里。纵横颠倒。而散布者。亦无不然。计其伏于土中者。累累皆是。有能以海涛荡涤漱雪。空岸土而尽出之。则不知当为几千百丛石。造物之巧。何以至此。奇哉奇哉。)亭后数十武许。有短碣委地。数字仅可识。世传四仙来游。而其徒立石志之云。西厓又有小亭将颓圮。可惜。风涛大作。不得汎舟丛石下。至于金襕窟。甚恨。小醉复临台。笑谓傍人曰米芾若拜如许石丈。则岂有遭弹哉。风霾甚冷。不能久坐。还到邑底。饭后即发。遵来时路行十五里许。有松林。昨薄暮径由林外相望处。今见其绵亘十数里。苍翠与海色相接。尽如三洲所记。惟昔之短小稚弱者。已经百岁。宜多虬枝铁干而却不然。岂或已作大厦栋梁欤。原野之𤄃远。实江陵以后始见。见其粳稻茂秀。可知非瘠土。而其不实有甚于横溪。野色青空。白死者十居八九。寔由广斥之壤。风损尤易也。揣想民情。行路伤恻。略被霏沾。行过一舍。川水大涨。桥梁尽坏。傍近村人迎护而渡。皆谓夜雨大注于金刚山侧。暮抵朝珍。巡行先已到。税良久矣。避馆中纷嚣。讨处稍僻。主人王姓有班名。问知先生台。相望甚迩。雨且暮未登观。夜无寐。主人略说风土习俗。蔀屋生涯。极艰楚。有葛屦履霜之叹。岁寒时雪堕如筛。顷刻间堆积
柱为体。石皆方直六面。其束皆整比如栉。类用绳尺刀钜为之者。不独四峰者然耳。其环亭数里。纵横颠倒。而散布者。亦无不然。计其伏于土中者。累累皆是。有能以海涛荡涤漱雪。空岸土而尽出之。则不知当为几千百丛石。造物之巧。何以至此。奇哉奇哉。)亭后数十武许。有短碣委地。数字仅可识。世传四仙来游。而其徒立石志之云。西厓又有小亭将颓圮。可惜。风涛大作。不得汎舟丛石下。至于金襕窟。甚恨。小醉复临台。笑谓傍人曰米芾若拜如许石丈。则岂有遭弹哉。风霾甚冷。不能久坐。还到邑底。饭后即发。遵来时路行十五里许。有松林。昨薄暮径由林外相望处。今见其绵亘十数里。苍翠与海色相接。尽如三洲所记。惟昔之短小稚弱者。已经百岁。宜多虬枝铁干而却不然。岂或已作大厦栋梁欤。原野之𤄃远。实江陵以后始见。见其粳稻茂秀。可知非瘠土。而其不实有甚于横溪。野色青空。白死者十居八九。寔由广斥之壤。风损尤易也。揣想民情。行路伤恻。略被霏沾。行过一舍。川水大涨。桥梁尽坏。傍近村人迎护而渡。皆谓夜雨大注于金刚山侧。暮抵朝珍。巡行先已到。税良久矣。避馆中纷嚣。讨处稍僻。主人王姓有班名。问知先生台。相望甚迩。雨且暮未登观。夜无寐。主人略说风土习俗。蔀屋生涯。极艰楚。有葛屦履霜之叹。岁寒时雪堕如筛。顷刻间堆积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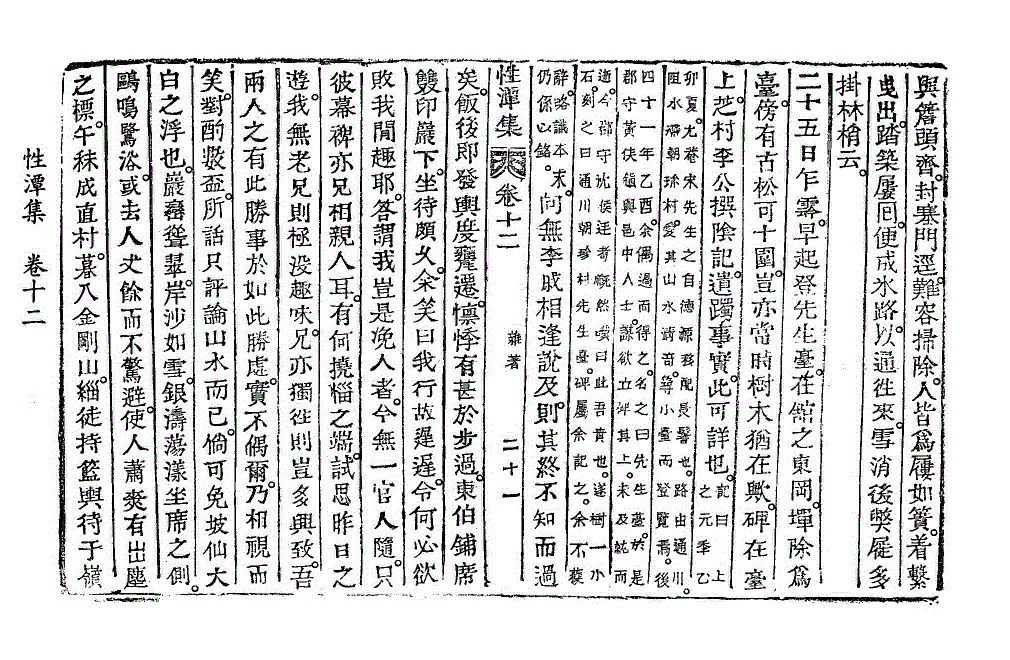 与檐头齐。封塞门径。难容扫除。人皆为屦如篑。着系曳出。踏筑屡回。便成冰路。以通往来。雪消后弊屣多挂林梢云。
与檐头齐。封塞门径。难容扫除。人皆为屦如篑。着系曳出。踏筑屡回。便成冰路。以通往来。雪消后弊屣多挂林梢云。二十五日乍𩃬。早起登先生台。在馆之东冈。墠除为台。傍有古松可十围。岂亦当时树木犹在欤。碑在台上。芝村李公撰阴记。遗躅事实。此可详也。(记曰 上之元季乙卯夏。尤庵宋先生之自德源移配长鬐也。路由通川。阻水滞朝珍村。爱其山水清奇。筑小台而登览焉。后四十一年乙酉。余偶过而得之。名之曰先生台。于是郡守黄侯镇与邑中人士。谋欲立碑其上。未及就而逝。今郡守沈侯廷耇慨然叹曰此吾责也。遂树一小石。刻之曰通川朝珍村先生台。碑属余记之。余不获辞。略识本末。仍系以铭。)向无李戚相逢说及。则其终不知而过矣。饭后即发舆度瓮迁。懔悸有甚于步过。东伯铺席双印岩下。坐待颇久。余笑曰我行故迟迟。令何必欲败我閒趣耶。答谓我岂是浼人者。今无一官人随。只彼幕裨亦兄相亲人耳。有何挠恼之端。试思昨日之游。我无老兄则极没趣味。兄亦独往则岂多兴致。吾两人之有此胜事于如此胜处。实不偶尔。乃相视而笑。对酌数杯。所话只评论山水而已。倘可免坡仙大白之浮也。岩峦耸翠。岸沙如雪。银涛荡漾坐席之侧。鸥鸣鹭浴。或去人丈馀而不惊避。使人萧爽有出尘之标。午秣成直村。暮入金刚山。缁徒持篮舆待于岭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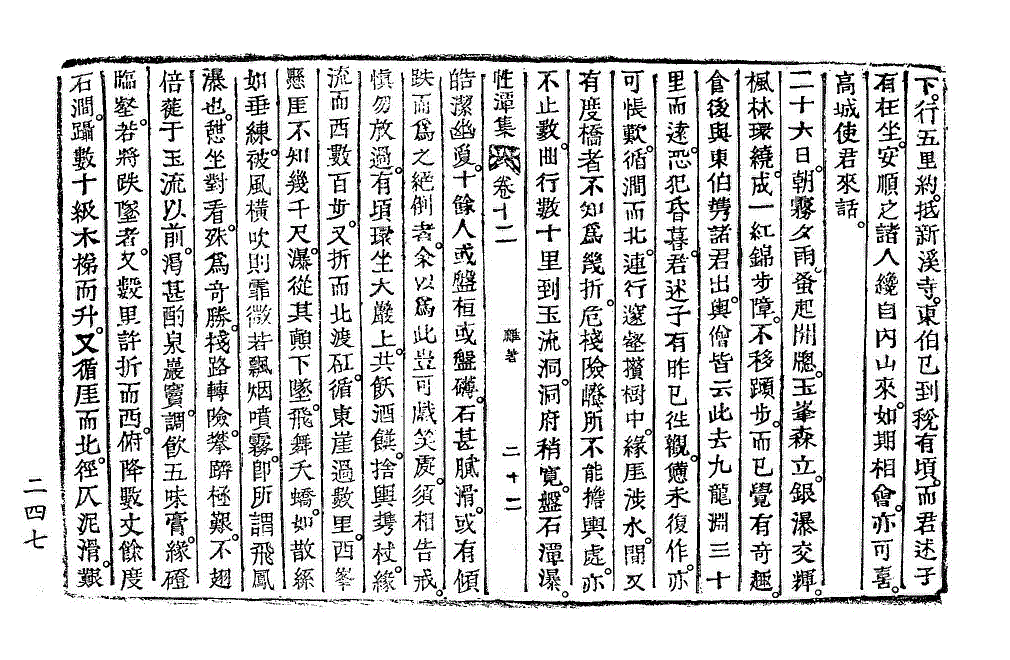 下。行五里约。抵新溪寺。东伯已到税有顷。而君述子有在坐。安顺之诸人才自内山来。如期相会。亦可喜。高城使君来话。
下。行五里约。抵新溪寺。东伯已到税有顷。而君述子有在坐。安顺之诸人才自内山来。如期相会。亦可喜。高城使君来话。二十六日。朝雾夕雨。蚤起开窗。玉峰森立。银瀑交辉。枫林环绕。成一红锦步障。不移跬步。而已觉有奇趣。食后与东伯携诸君出。舆僧皆云此去九龙渊三十里而远。恐犯昏暮。君述子有昨已往观。惫未复作。亦可怅叹。循涧而北。连行邃壑攒树中。缘厓涉水。间又有度桥者不知为几折。危栈险嶝所不能担舆处。亦不止数。曲行数十里到玉流洞。洞府稍宽。盘石潭瀑。皓洁幽夐。十馀人或盘桓或盘礴。石甚腻滑。或有倾跌而为之绝倒者。余以为此岂可戏笑处。须相告戒。慎勿放过。有顷环坐大岩上。共饫酒馔。舍舆携杖。缘流而西数百步。又折而北渡矼。循东崖过数里。西峰悬厓不知几千尺。瀑从其颠下坠。飞舞夭蟜。如散丝如垂练。被风横吹则霏微若飘烟喷雾。即所谓飞凤瀑也。憩坐对看。殊为奇胜。栈路转险。攀跻极艰。不翅倍蓰于玉流以前。渴甚酌泉岩窦。调饮五味膏。缘磴临壑。若将跌坠者。又数里许折而西。俯降数丈馀度石涧。蹑数十级木梯而升。又循厓而北。径仄泥滑。艰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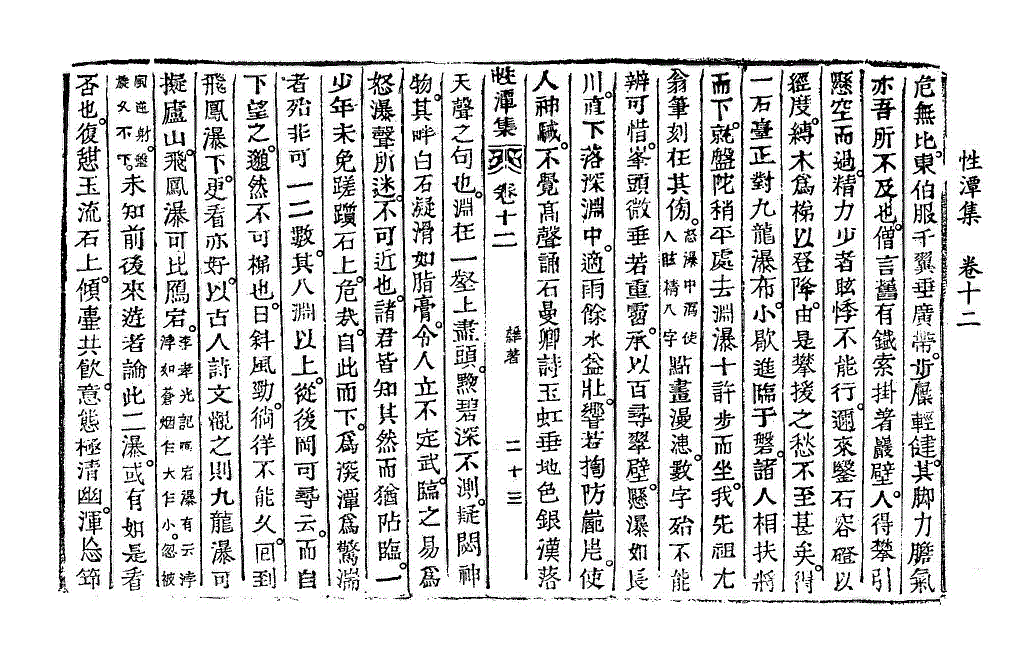 危无比。东伯服千翼垂广带。步屧轻健。其脚力胆气亦吾所不及也。僧言旧有铁索挂着岩壁。人得攀引悬空而过。精力少者眩悸不能行。迩来凿石容磴以经度。缚木为梯以登降。由是攀援之愁不至甚矣。得一石台正对九龙瀑布。小歇进临于磐。诸人相扶将而下。就盘陀稍平处去渊瀑十许步而坐。我先祖尤翁笔刻在其傍。(怒瀑中泻使人眩精八字。)点画漫漶。数字殆不能辨可惜。峰头微垂若重霤。承以百寻翠壁。悬瀑如长川。直下落深渊中。适雨馀水益壮。响若轰防嶏岸。使人神駴。不觉高声诵石曼卿诗玉虹垂地色银汉落天声之句也。渊在一壑上尽头。黝碧深不测。疑閟神物。其畔白石凝滑如脂膏。令人立不定武。临之易为怒瀑声所迷。不可近也。诸君皆知其然而犹阽临。一少年未免蹉踬石上。危哉。自此而下。为深潭为惊湍者殆非可一二数。其八渊以上。从后冈可寻云。而自下望之。邈然不可梯也。日斜风劲。徜徉不能久。回到飞凤瀑下。更看亦好。以古人诗文观之则九龙瀑可拟庐山。飞凤瀑可比雁宕。(李孝光记雁宕瀑有云浡浡如苍烟乍大乍小。忽被风逆射。盘旋久不下。)未知前后来游者论此二瀑。或有如是看否也。复憩玉流石上。倾壶共饮。意态极清幽。浑忘筇
危无比。东伯服千翼垂广带。步屧轻健。其脚力胆气亦吾所不及也。僧言旧有铁索挂着岩壁。人得攀引悬空而过。精力少者眩悸不能行。迩来凿石容磴以经度。缚木为梯以登降。由是攀援之愁不至甚矣。得一石台正对九龙瀑布。小歇进临于磐。诸人相扶将而下。就盘陀稍平处去渊瀑十许步而坐。我先祖尤翁笔刻在其傍。(怒瀑中泻使人眩精八字。)点画漫漶。数字殆不能辨可惜。峰头微垂若重霤。承以百寻翠壁。悬瀑如长川。直下落深渊中。适雨馀水益壮。响若轰防嶏岸。使人神駴。不觉高声诵石曼卿诗玉虹垂地色银汉落天声之句也。渊在一壑上尽头。黝碧深不测。疑閟神物。其畔白石凝滑如脂膏。令人立不定武。临之易为怒瀑声所迷。不可近也。诸君皆知其然而犹阽临。一少年未免蹉踬石上。危哉。自此而下。为深潭为惊湍者殆非可一二数。其八渊以上。从后冈可寻云。而自下望之。邈然不可梯也。日斜风劲。徜徉不能久。回到飞凤瀑下。更看亦好。以古人诗文观之则九龙瀑可拟庐山。飞凤瀑可比雁宕。(李孝光记雁宕瀑有云浡浡如苍烟乍大乍小。忽被风逆射。盘旋久不下。)未知前后来游者论此二瀑。或有如是看否也。复憩玉流石上。倾壶共饮。意态极清幽。浑忘筇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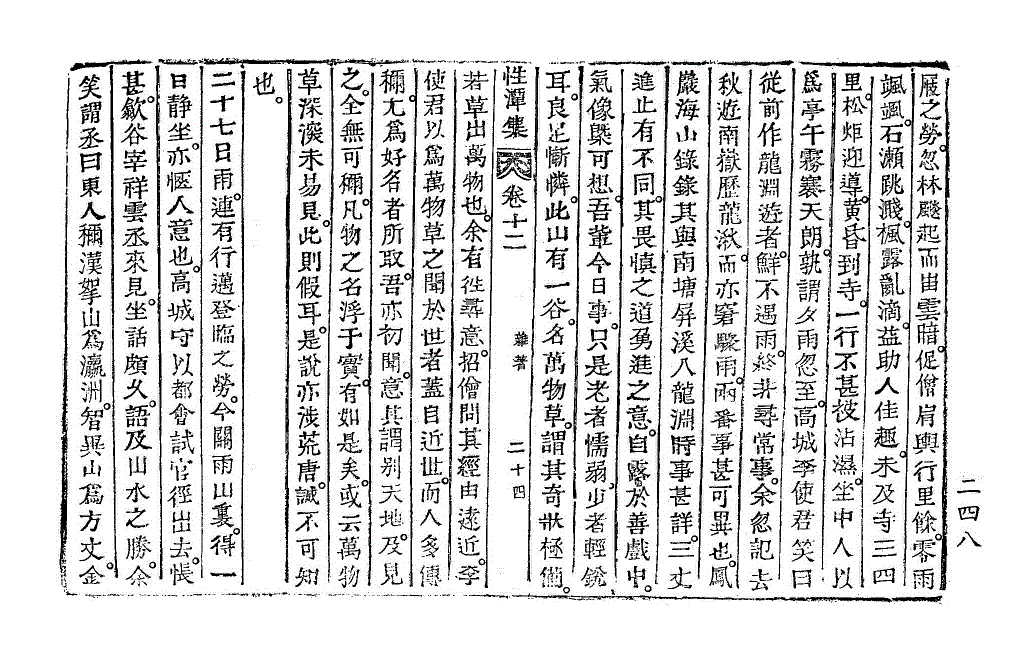 屐之劳。忽林飙起而岫云暗。促僧肩舆行里馀。零雨飒飒。石濑跳溅。枫露乱滴。益助人佳趣。未及寺三四里。松炬迎导。黄昏到寺。一行不甚被沾湿。坐中人以为亭午雾褰天朗。孰谓夕雨忽至。高城李使君笑曰从前作龙渊游者。鲜不遇雨。终非寻常事。余忽记去秋游南岳历龙湫。而亦窘骤雨。两番事甚可异也。凤岩海山录录其与南塘屏溪入龙渊时事甚详。三丈进止有不同。其畏慎之道勇进之意。自露于善戏中。气像槩可想。吾辈今日事。只是老者懦弱。少者轻锐耳。良足惭怜。此山有一谷。名万物草。谓其奇状极备。若草出万物也。余有往寻意。招僧问其经由远近。李使君以为万物草之闻于世者盖自近世。而人多传称。尤为好名者所取。吾亦初闻。意其谓别天地。及见之。全无可称。凡物之名浮于实。有如是矣。或云万物草深深未易见。此则假耳。是说亦涉荒唐。诚不可知也。
屐之劳。忽林飙起而岫云暗。促僧肩舆行里馀。零雨飒飒。石濑跳溅。枫露乱滴。益助人佳趣。未及寺三四里。松炬迎导。黄昏到寺。一行不甚被沾湿。坐中人以为亭午雾褰天朗。孰谓夕雨忽至。高城李使君笑曰从前作龙渊游者。鲜不遇雨。终非寻常事。余忽记去秋游南岳历龙湫。而亦窘骤雨。两番事甚可异也。凤岩海山录录其与南塘屏溪入龙渊时事甚详。三丈进止有不同。其畏慎之道勇进之意。自露于善戏中。气像槩可想。吾辈今日事。只是老者懦弱。少者轻锐耳。良足惭怜。此山有一谷。名万物草。谓其奇状极备。若草出万物也。余有往寻意。招僧问其经由远近。李使君以为万物草之闻于世者盖自近世。而人多传称。尤为好名者所取。吾亦初闻。意其谓别天地。及见之。全无可称。凡物之名浮于实。有如是矣。或云万物草深深未易见。此则假耳。是说亦涉荒唐。诚不可知也。二十七日雨。连有行迈登临之劳。今关雨山里。得一日静坐。亦惬人意也。高城守以都会试官径出去。怅甚。歙谷宰祥云丞来见。坐话颇久。语及山水之胜。余笑谓丞曰东人称汉挐山为瀛洲。智异山为方丈。金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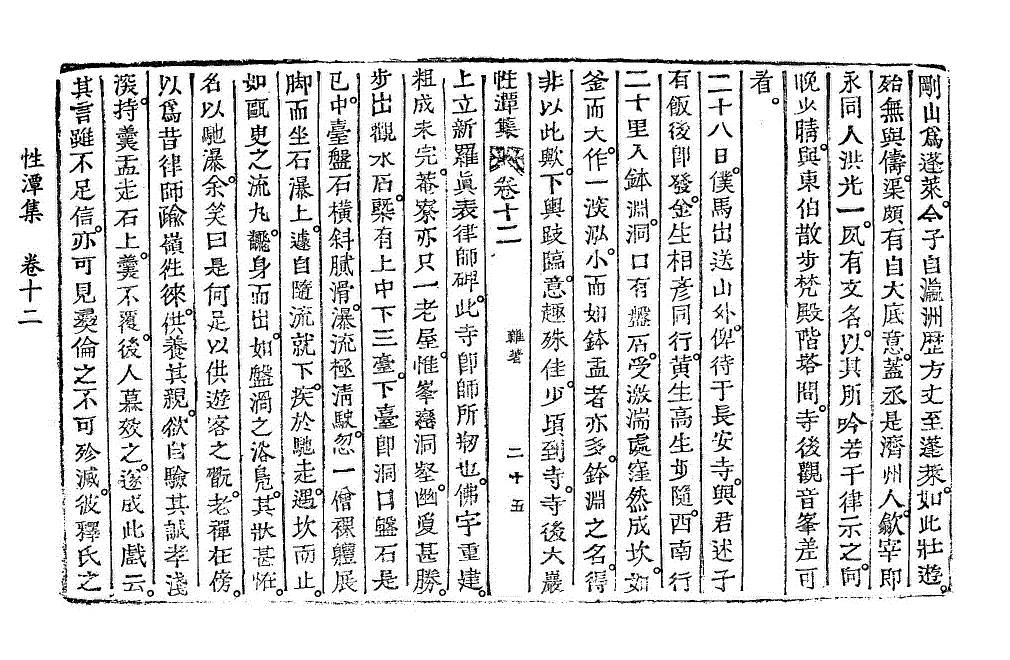 刚山为蓬莱。今子自瀛洲历方丈至蓬莱。如此壮游。殆无与俦。渠颇有自大底意。盖丞是济州人。歙宰即永同人洪光一。夙有文名。以其所吟若干律示之。向晚少晴。与东伯散步梵殿阶塔间。寺后观音峰差可看。
刚山为蓬莱。今子自瀛洲历方丈至蓬莱。如此壮游。殆无与俦。渠颇有自大底意。盖丞是济州人。歙宰即永同人洪光一。夙有文名。以其所吟若干律示之。向晚少晴。与东伯散步梵殿阶塔间。寺后观音峰差可看。二十八日。仆马出送山外。俾待于长安寺。与君述子有饭后即发。金生相彦同行。黄生高生步随。西南行二十里入钵渊。洞口有盘石。受激湍处洼然成坎。如釜而大。作一深泓。小而如钵盂者亦多。钵渊之名。得非以此欤。下舆跂临。意趣殊佳。少顷到寺。寺后大岩上立新罗真表律师碑。此寺即师所刱也。佛宇重建。粗成未完。庵寮亦只一老屋。惟峰峦洞壑。幽夐甚胜。步出观水石。槩有上中下三台。下台即洞口盘石是已。中台盘石横斜腻滑。瀑流极清驶。忽一僧裸体展脚而坐石瀑上。遽自随流就下。疾于驰走。遇坎而止。如瓯臾之流丸。翻身而出。如盘涡之浴凫。其状甚怪。名以驰瀑。余笑曰是何足以供游客之玩。老禅在傍。以为昔律师踰岭往徕。供养其亲。欲自验其诚孝浅深。持羹盂走石上。羹不覆。后人慕效之。遂成此戏云。其言虽不足信。亦可见彝伦之不可殄灭。彼释氏之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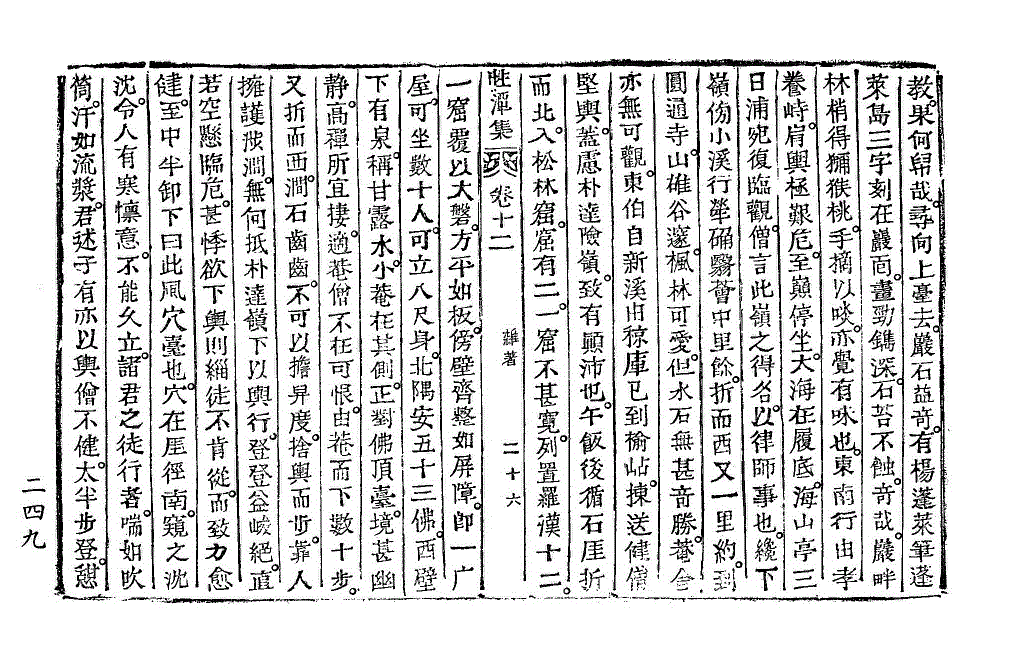 教。果何帠哉。寻向上台去。岩石益奇。有杨蓬莱笔蓬莱岛三字刻在岩面。画劲镌深。石苔不蚀。奇哉。岩畔林梢得猕猴桃。手摘以啖。亦觉有味也。东南行由孝养峙。肩舆极艰危。至巅停坐。大海在履底。海山亭三日浦宛复临观。僧言此岭之得名。以律师事也。才下岭傍小溪行荦确翳荟中里馀。折而西又一里约。到圆通寺。山雄谷邃。枫林可爱。但水石无甚奇胜。庵舍亦无可观。东伯自新溪由稤库已到榆岾。拣送健僧坚舆。盖虑朴达险岭。致有颠沛也。午饭后循石厓折而北。入松林窟。窟有二。一窟不甚宽。列置罗汉十二。一窟覆以大磐。方平如板。傍壁齐整如屏障。即一广屋。可坐数十人。可立八尺身。北隅安五十三佛。西壁下有泉。称甘露水。小庵在其侧。正对佛顶台。境甚幽静。高禅所宜栖。适庵僧不在可恨。由庵而下数十步。又折而西。涧石齿齿。不可以担舁度。舍舆而步。靠人拥护涉涧。无何抵朴达岭下以舆行。登登益峻绝。直若空悬临危。甚悸欲下舆则缁徒不肯从。而致力愈健。至中半卸下曰此风穴台也。穴在厓径南。窥之沈沈。令人有寒懔意。不能久立。诸君之徒行者。喘如吹筒。汗如流浆。君述子有亦以舆僧不健。太半步登。憩
教。果何帠哉。寻向上台去。岩石益奇。有杨蓬莱笔蓬莱岛三字刻在岩面。画劲镌深。石苔不蚀。奇哉。岩畔林梢得猕猴桃。手摘以啖。亦觉有味也。东南行由孝养峙。肩舆极艰危。至巅停坐。大海在履底。海山亭三日浦宛复临观。僧言此岭之得名。以律师事也。才下岭傍小溪行荦确翳荟中里馀。折而西又一里约。到圆通寺。山雄谷邃。枫林可爱。但水石无甚奇胜。庵舍亦无可观。东伯自新溪由稤库已到榆岾。拣送健僧坚舆。盖虑朴达险岭。致有颠沛也。午饭后循石厓折而北。入松林窟。窟有二。一窟不甚宽。列置罗汉十二。一窟覆以大磐。方平如板。傍壁齐整如屏障。即一广屋。可坐数十人。可立八尺身。北隅安五十三佛。西壁下有泉。称甘露水。小庵在其侧。正对佛顶台。境甚幽静。高禅所宜栖。适庵僧不在可恨。由庵而下数十步。又折而西。涧石齿齿。不可以担舁度。舍舆而步。靠人拥护涉涧。无何抵朴达岭下以舆行。登登益峻绝。直若空悬临危。甚悸欲下舆则缁徒不肯从。而致力愈健。至中半卸下曰此风穴台也。穴在厓径南。窥之沈沈。令人有寒懔意。不能久立。诸君之徒行者。喘如吹筒。汗如流浆。君述子有亦以舆僧不健。太半步登。憩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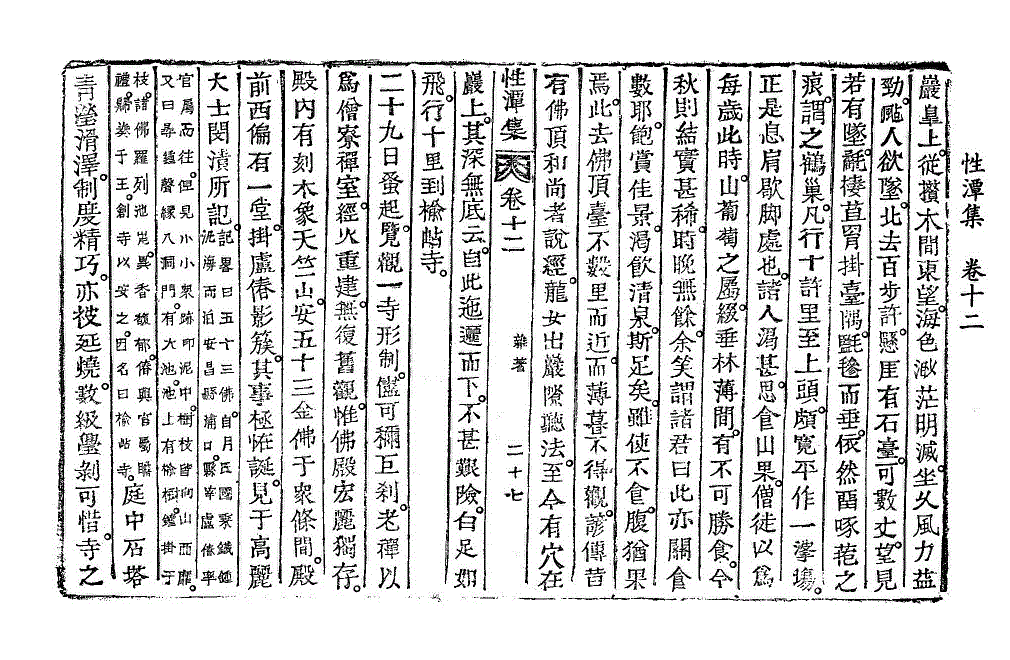 岩皋上。从攒木间东望。海色渺茫明灭。坐久风力益劲。飐人欲坠。北去百步许。悬厓有石台。可数丈。望见若有坠。氄栖苴罥挂台隅。㲯𣯶而垂。依然留啄抱之痕。谓之鹤巢。凡行十许里至上头。颇宽平作一搫场。正是息肩歇脚处也。诸人渴甚。思食山果。僧徒以为每岁此时。山葡萄之属。缀垂林薄间。有不可胜食。今秋则结实甚稀。时晚无馀。余笑谓诸君曰此亦关食数耶。饱赏佳景。渴饮清泉。斯足矣。虽使不食。腹犹果焉。此去佛顶台不数里而近。而薄暮不得观。谚传昔有佛顶和尚者说经。龙女出岩隙听法。至今有穴在岩上。其深无底云。自此迤逦而下。不甚艰险。白足如飞。行十里到榆岾寺。
岩皋上。从攒木间东望。海色渺茫明灭。坐久风力益劲。飐人欲坠。北去百步许。悬厓有石台。可数丈。望见若有坠。氄栖苴罥挂台隅。㲯𣯶而垂。依然留啄抱之痕。谓之鹤巢。凡行十许里至上头。颇宽平作一搫场。正是息肩歇脚处也。诸人渴甚。思食山果。僧徒以为每岁此时。山葡萄之属。缀垂林薄间。有不可胜食。今秋则结实甚稀。时晚无馀。余笑谓诸君曰此亦关食数耶。饱赏佳景。渴饮清泉。斯足矣。虽使不食。腹犹果焉。此去佛顶台不数里而近。而薄暮不得观。谚传昔有佛顶和尚者说经。龙女出岩隙听法。至今有穴在岩上。其深无底云。自此迤逦而下。不甚艰险。白足如飞。行十里到榆岾寺。二十九日蚤起。览观一寺形制。尽可称巨刹。老禅以为僧寮禅室。经火重建。无复旧观。惟佛殿宏丽独存。殿内有刻木象天竺山。安五十三金佛于众条间。殿前西偏有一堂。挂卢偆影簇。其事极怪诞。见于高丽大士闵渍所记。(记略曰五十三佛。自月氏国乘铁钟汎海而泊安昌县浦口。县宰卢偆率官属而往。但见小小众迹印泥中。树枝皆向山西靡。又曰寻钟声缘入洞门。有大池。池上有榆树。钟挂于枝。诸佛罗列池岸。异香馥郁。偆与官属瞻礼。归奏于王。创寺以安之。因名曰榆岾寺。)庭中石塔青莹滑泽。制度精巧。亦被延烧。数级璺剥可惜。寺之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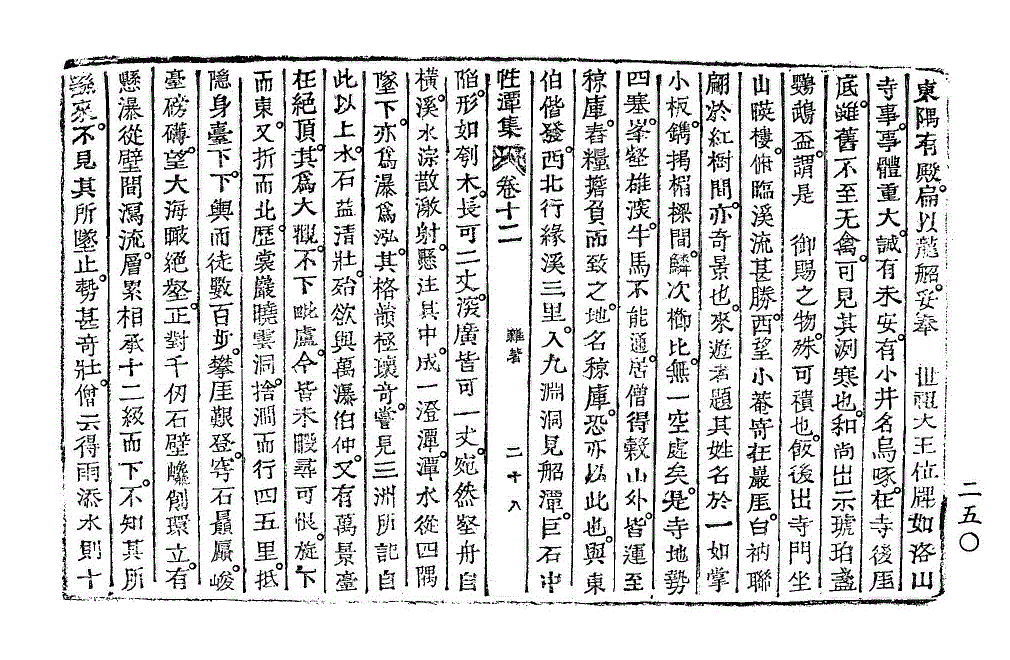 东隅有殿。扁以龙𦨣。妥奉 世祖大王位牌如洛山寺事。事体重大。诚有未安。有小井名乌啄。在寺后厓底。虽旧不至无禽。可见其洌寒也。和尚出示琥珀盏鹦鹉杯。谓是 御赐之物。殊可贵也。饭后出寺门坐山映楼。俯临溪流甚胜。西望小庵寄在岩厓。白衲联翩于红树间。亦奇景也。来游者题其姓名于一如掌小板。镌揭楣梁间。鳞次栉比。无一空处矣。是寺地势四塞。峰壑雄深。牛马不能通。居僧得谷山外。皆运至稤库。舂粮担负而致之。地名稤库。恐亦以此也。与东伯偕发。西北行缘溪三里。入九渊洞见𦨣潭。巨石中陷。形如刳木。长可二丈。深广皆可一丈。宛然壑舟自横。溪水淙散激射。悬注其中。成一澄潭。潭水从四隅坠下。亦为瀑为泓。其格韵极瑰奇。尝见三洲所记自此以上。水石益清壮。殆欲与万瀑伯仲。又有万景台在绝顶。其为大观。不下毗卢。今皆未暇寻可恨。旋下而东。又折而北。历裳岩晓云洞。舍涧而行四五里。抵隐身台下。下舆而徒数百步。攀厓艰登。穹石赑屃。峻台磅礴。望大海瞰绝壑。正对千仞石壁巉削环立。有悬瀑从壁间泻流。层累相承十二级而下。不知其所繇来。不见其所坠止。势甚奇壮。僧云得雨添水则十
东隅有殿。扁以龙𦨣。妥奉 世祖大王位牌如洛山寺事。事体重大。诚有未安。有小井名乌啄。在寺后厓底。虽旧不至无禽。可见其洌寒也。和尚出示琥珀盏鹦鹉杯。谓是 御赐之物。殊可贵也。饭后出寺门坐山映楼。俯临溪流甚胜。西望小庵寄在岩厓。白衲联翩于红树间。亦奇景也。来游者题其姓名于一如掌小板。镌揭楣梁间。鳞次栉比。无一空处矣。是寺地势四塞。峰壑雄深。牛马不能通。居僧得谷山外。皆运至稤库。舂粮担负而致之。地名稤库。恐亦以此也。与东伯偕发。西北行缘溪三里。入九渊洞见𦨣潭。巨石中陷。形如刳木。长可二丈。深广皆可一丈。宛然壑舟自横。溪水淙散激射。悬注其中。成一澄潭。潭水从四隅坠下。亦为瀑为泓。其格韵极瑰奇。尝见三洲所记自此以上。水石益清壮。殆欲与万瀑伯仲。又有万景台在绝顶。其为大观。不下毗卢。今皆未暇寻可恨。旋下而东。又折而北。历裳岩晓云洞。舍涧而行四五里。抵隐身台下。下舆而徒数百步。攀厓艰登。穹石赑屃。峻台磅礴。望大海瞰绝壑。正对千仞石壁巉削环立。有悬瀑从壁间泻流。层累相承十二级而下。不知其所繇来。不见其所坠止。势甚奇壮。僧云得雨添水则十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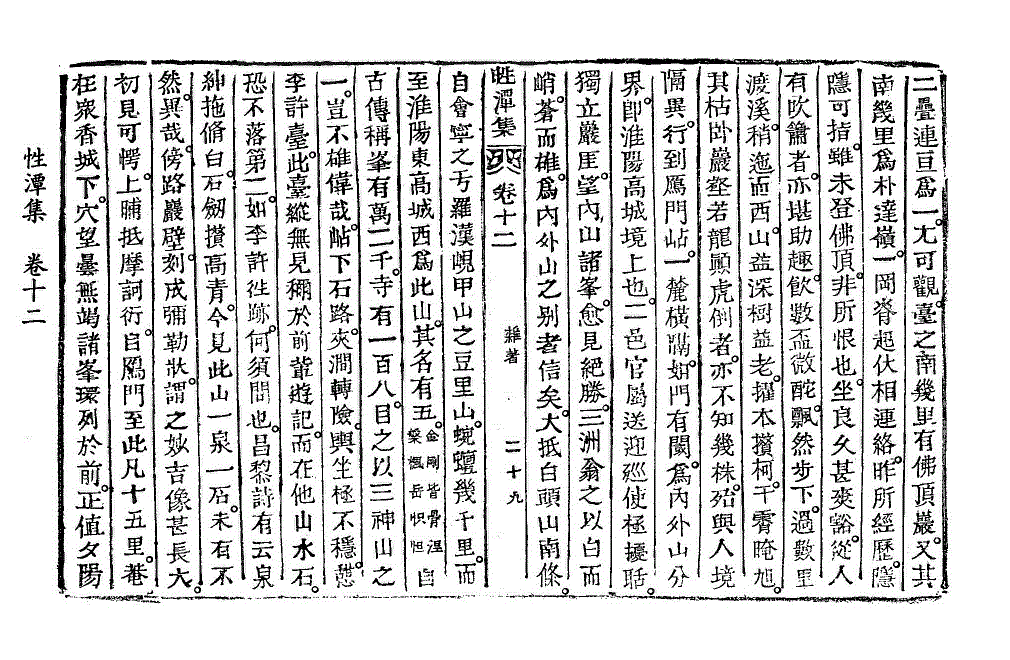 二叠连亘为一。尤可观。台之南几里有佛顶岩。又其南几里为朴达岭。一冈脊起伏相连络。昨所经历。隐隐可指。虽未登佛顶。非所恨也。坐良久甚爽豁。从人有吹箫者。亦堪助趣。饮数杯微酡。飘然步下。过数里渡溪。稍迤而西。山益深树益老。擢本攒柯。干霄晻旭。其枯卧岩壑若龙颠虎倒者。亦不知几株。殆与人境隔异。行到雁门岾。一麓横隔。如门有阈。为内外山分界。即淮阳高城境上也。二邑官属送迎巡使极扰聒。独立岩厓。望内山诸峰。愈见绝胜。三洲翁之以白而峭。苍而雄。为内外山之别者信矣。大抵白头山南条。自会宁之于罗汉岘甲山之豆里山。蜿蟺几千里。而至淮阳东高城西为此山。其名有五。(金刚皆骨涅槃枫岳怾怛。)自古传称峰有万二千。寺有一百八。目之以三神山之一。岂不雄伟哉。岾下石路。夹涧转险。舆坐极不稳。憩李许台。此台纵无见称于前辈游记。而在他山水石。恐不落第二。如李许往迹。何须问也。昌黎诗有云泉绅拖脩白。石剑攒高青。今见此山一泉一石。未有不然。异哉。傍路岩壁。刻成弥勒状。谓之妙吉像甚长大。初见可愕。上晡抵摩诃衍。自雁门至此凡十五里。庵在众香城下。穴望昙无竭诸峰环列于前。正值夕阳
二叠连亘为一。尤可观。台之南几里有佛顶岩。又其南几里为朴达岭。一冈脊起伏相连络。昨所经历。隐隐可指。虽未登佛顶。非所恨也。坐良久甚爽豁。从人有吹箫者。亦堪助趣。饮数杯微酡。飘然步下。过数里渡溪。稍迤而西。山益深树益老。擢本攒柯。干霄晻旭。其枯卧岩壑若龙颠虎倒者。亦不知几株。殆与人境隔异。行到雁门岾。一麓横隔。如门有阈。为内外山分界。即淮阳高城境上也。二邑官属送迎巡使极扰聒。独立岩厓。望内山诸峰。愈见绝胜。三洲翁之以白而峭。苍而雄。为内外山之别者信矣。大抵白头山南条。自会宁之于罗汉岘甲山之豆里山。蜿蟺几千里。而至淮阳东高城西为此山。其名有五。(金刚皆骨涅槃枫岳怾怛。)自古传称峰有万二千。寺有一百八。目之以三神山之一。岂不雄伟哉。岾下石路。夹涧转险。舆坐极不稳。憩李许台。此台纵无见称于前辈游记。而在他山水石。恐不落第二。如李许往迹。何须问也。昌黎诗有云泉绅拖脩白。石剑攒高青。今见此山一泉一石。未有不然。异哉。傍路岩壁。刻成弥勒状。谓之妙吉像甚长大。初见可愕。上晡抵摩诃衍。自雁门至此凡十五里。庵在众香城下。穴望昙无竭诸峰环列于前。正值夕阳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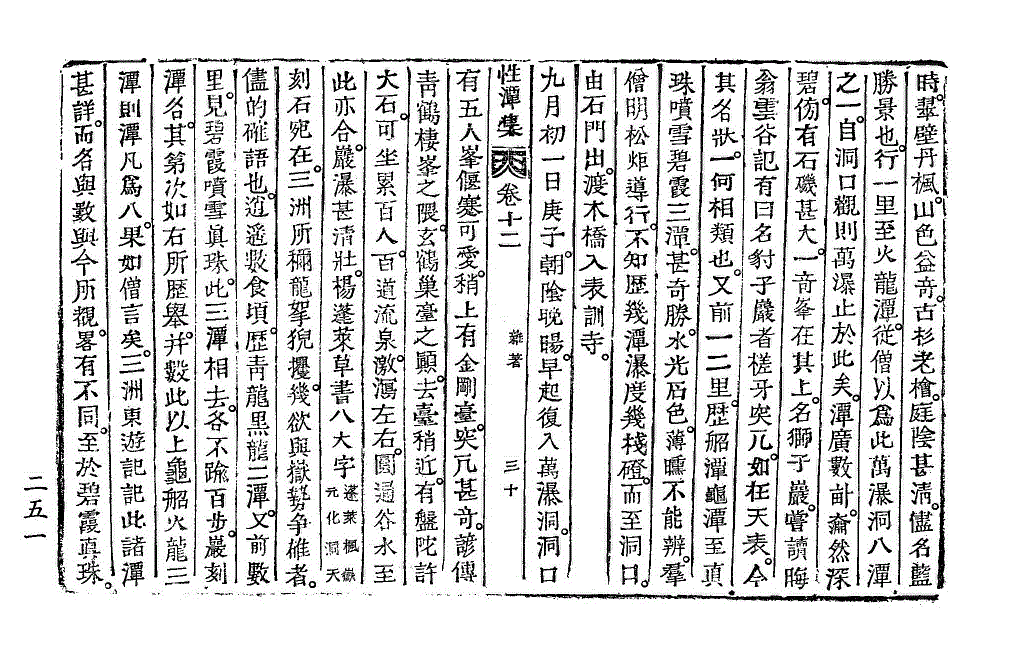 时。翠壁丹枫。山色益奇。古杉老桧。庭阴甚清。尽名蓝胜景也。行一里至火龙潭。从僧以为此万瀑洞八潭之一。自洞口观则万瀑止于此矣。潭广数亩。奫然深碧。傍有石矶甚大。一奇峰在其上。名狮子岩。尝读晦翁云谷记有曰名豺子岩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今其名状。一何相类也。又前一二里。历𦨣潭龟潭至真珠喷雪碧霞三潭。甚奇胜。水光石色。薄曛不能辨。群僧明松炬导行。不知历几潭瀑度几栈磴。而至洞口。由石门出。渡木桥入表训寺。
时。翠壁丹枫。山色益奇。古杉老桧。庭阴甚清。尽名蓝胜景也。行一里至火龙潭。从僧以为此万瀑洞八潭之一。自洞口观则万瀑止于此矣。潭广数亩。奫然深碧。傍有石矶甚大。一奇峰在其上。名狮子岩。尝读晦翁云谷记有曰名豺子岩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今其名状。一何相类也。又前一二里。历𦨣潭龟潭至真珠喷雪碧霞三潭。甚奇胜。水光石色。薄曛不能辨。群僧明松炬导行。不知历几潭瀑度几栈磴。而至洞口。由石门出。渡木桥入表训寺。九月初一日庚子。朝阴晚旸。早起复入万瀑洞。洞口有五人峰偃蹇可爱。稍上有金刚台。突兀甚奇。谚传青鹤栖峰之隈。玄鹤巢台之颠。去台稍近。有盘陀许大石。可坐累百人。百道流泉。激泻左右。圆通谷水至此亦合。岩瀑甚清壮。杨蓬莱草书八大字(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刻石宛在。三洲所称龙挐猊攫。几欲与岳势争雄者。尽的确语也。逍遥数食顷。历青龙黑龙二潭。又前数里。见碧霞喷雪真珠。此三潭相去。各不踰百步。岩刻潭名。其第次如右所历举。并数此以上龟𦨣火龙三潭则潭凡为八。果如僧言矣。三洲东游记记此诸潭甚详。而名与数与今所睹。略有不同。至于碧霞真珠。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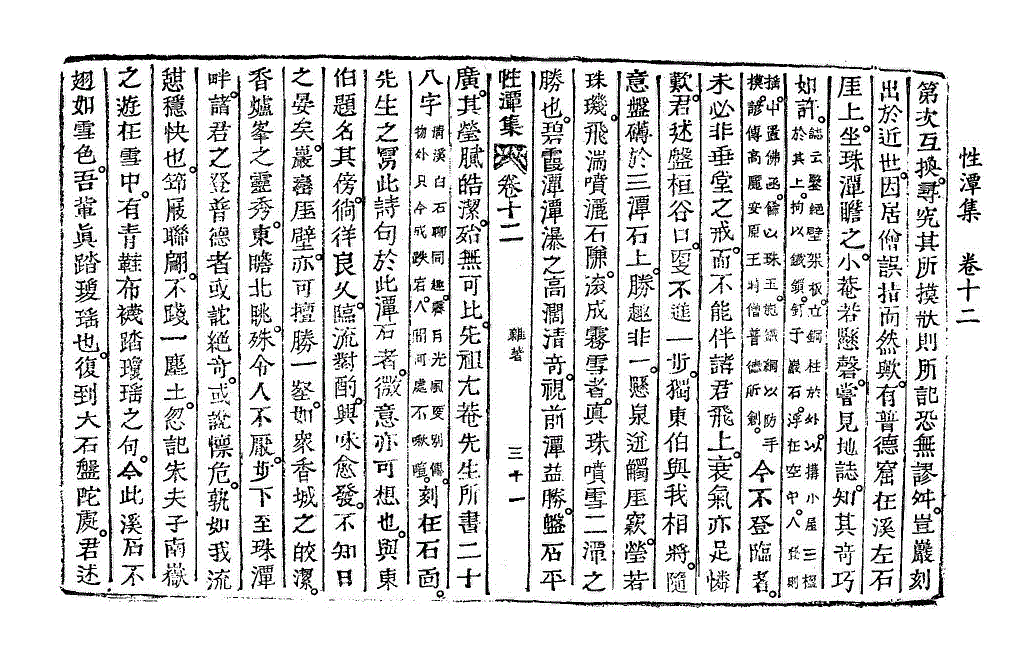 第次互换。寻究其所摸状则所记恐无谬舛。岂岩刻出于近世。因居僧误指而然欤。有普德窟在溪左石厓上。坐珠潭瞻之。小庵若悬磬。尝见地志。知其奇巧如许。(志云凿绝壁架板。立铜柱于外。以搆小屋三楹于其上。拘以铁锁。钉于岩石。浮在空中。人登则摇。中置佛函。饰以珠玉。施铁网以防手摸。谚传高丽安原王时僧普德所创。)今不登临者。未必非垂堂之戒。而不能伴诸君飞上。衰气亦足怜叹。君述盘桓谷口。更不进一步。独东伯与我相将。随意盘礴于三潭石上。胜趣非一。悬泉迸触厓窾。莹若珠玑。飞湍喷洒石隒。滚成雾雪者。真珠喷雪二潭之胜也。碧霞潭潭瀑之高阔清奇。视前潭益胜。盘石平广。其莹腻皓洁。殆无可比。先祖尤庵先生所书二十八字(清溪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刻在石面。先生之写此诗句于此潭石者。微意亦可想也。与东伯题名其傍。徜徉良久。临流对酌。兴味愈发。不知日之晏矣。岩峦厓壁。亦可擅胜一壑。如众香城之皎洁。香炉峰之灵秀。东瞻北眺。殊令人不厌。步下至珠潭畔。诸君之登普德者或詑绝奇。或说懔危。孰如我流憩稳快也。筇屐联翩。不践一尘土。忽记朱夫子南岳之游在雪中。有青鞋布袜踏琼瑶之句。今此溪石不翅如雪色。吾辈真踏琼瑶也。复到大石盘陀处。君述
第次互换。寻究其所摸状则所记恐无谬舛。岂岩刻出于近世。因居僧误指而然欤。有普德窟在溪左石厓上。坐珠潭瞻之。小庵若悬磬。尝见地志。知其奇巧如许。(志云凿绝壁架板。立铜柱于外。以搆小屋三楹于其上。拘以铁锁。钉于岩石。浮在空中。人登则摇。中置佛函。饰以珠玉。施铁网以防手摸。谚传高丽安原王时僧普德所创。)今不登临者。未必非垂堂之戒。而不能伴诸君飞上。衰气亦足怜叹。君述盘桓谷口。更不进一步。独东伯与我相将。随意盘礴于三潭石上。胜趣非一。悬泉迸触厓窾。莹若珠玑。飞湍喷洒石隒。滚成雾雪者。真珠喷雪二潭之胜也。碧霞潭潭瀑之高阔清奇。视前潭益胜。盘石平广。其莹腻皓洁。殆无可比。先祖尤庵先生所书二十八字(清溪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刻在石面。先生之写此诗句于此潭石者。微意亦可想也。与东伯题名其傍。徜徉良久。临流对酌。兴味愈发。不知日之晏矣。岩峦厓壁。亦可擅胜一壑。如众香城之皎洁。香炉峰之灵秀。东瞻北眺。殊令人不厌。步下至珠潭畔。诸君之登普德者或詑绝奇。或说懔危。孰如我流憩稳快也。筇屐联翩。不践一尘土。忽记朱夫子南岳之游在雪中。有青鞋布袜踏琼瑶之句。今此溪石不翅如雪色。吾辈真踏琼瑶也。复到大石盘陀处。君述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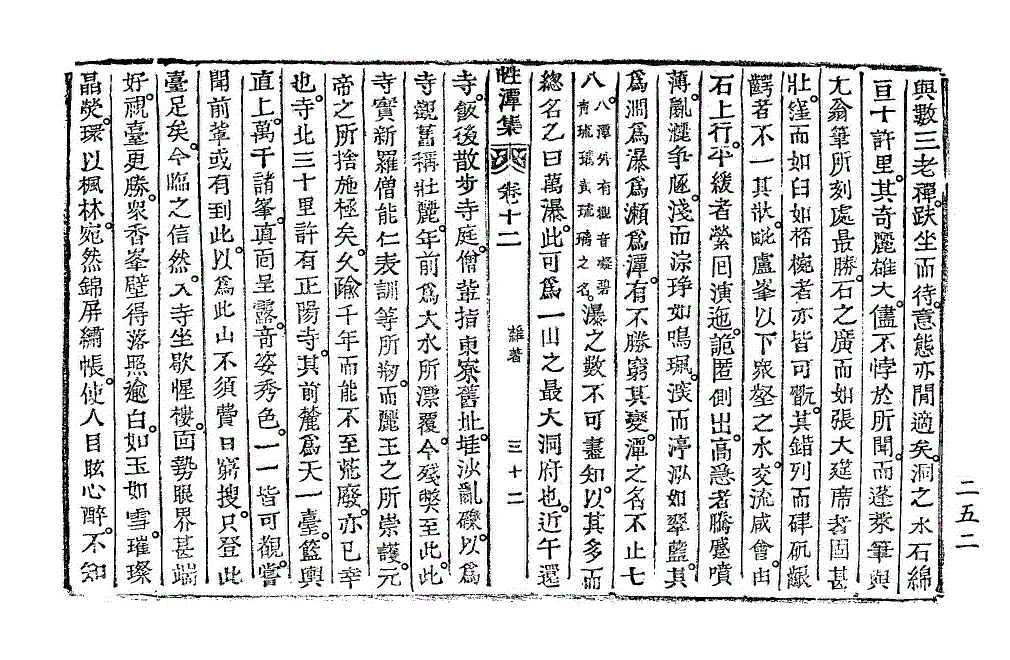 与数三老禅。趺坐而待。意态亦閒适矣。洞之水石绵亘十许里。其奇丽雄大。尽不悖于所闻。而蓬莱笔与尤翁笔所刻处最胜。石之广而如张大筵席者固甚壮。洼而如臼如杯碗者亦皆可玩。其错列而硉矹龈腭者不一其状。毗卢峰以下众壑之水。交流咸会。由石上行。平缓者萦回演迤。诡匿侧出。高急者腾蹙喷薄。乱洒争豗。浅而淙琤如鸣佩。深而渟泓如翠蓝。其为涧为瀑为濑为潭。有不胜穷其变。潭之名不止七八。(八潭外有观音凝碧青琉璃黄琉璃之名。)瀑之数不可尽知。以其多而总名之曰万瀑。此可为一山之最大洞府也。近午还寺。饭后散步寺庭。僧辈指东寮旧址。堆沙乱砾。以为寺观旧称壮丽。年前为大水所漂覆。今残弊至此。此寺实新罗僧能仁表训等所刱。而丽王之所崇护。元帝之所舍施极矣。久踰千年而能不至荒废。亦已幸也。寺北三十里许有正阳寺。其前麓为天一台。篮舆直上。万千诸峰。真面呈露。奇姿秀色。一一皆可睹。尝闻前辈或有到此。以为此山不须费日穷搜。只登此台足矣。今临之信然。入寺坐歇惺楼。面势眼界甚端好。视台更胜。众香峰壁得落照逾白。如玉如雪。璀璨晶荧。环以枫林。宛然锦屏绣帐。使人目眩心醉。不知
与数三老禅。趺坐而待。意态亦閒适矣。洞之水石绵亘十许里。其奇丽雄大。尽不悖于所闻。而蓬莱笔与尤翁笔所刻处最胜。石之广而如张大筵席者固甚壮。洼而如臼如杯碗者亦皆可玩。其错列而硉矹龈腭者不一其状。毗卢峰以下众壑之水。交流咸会。由石上行。平缓者萦回演迤。诡匿侧出。高急者腾蹙喷薄。乱洒争豗。浅而淙琤如鸣佩。深而渟泓如翠蓝。其为涧为瀑为濑为潭。有不胜穷其变。潭之名不止七八。(八潭外有观音凝碧青琉璃黄琉璃之名。)瀑之数不可尽知。以其多而总名之曰万瀑。此可为一山之最大洞府也。近午还寺。饭后散步寺庭。僧辈指东寮旧址。堆沙乱砾。以为寺观旧称壮丽。年前为大水所漂覆。今残弊至此。此寺实新罗僧能仁表训等所刱。而丽王之所崇护。元帝之所舍施极矣。久踰千年而能不至荒废。亦已幸也。寺北三十里许有正阳寺。其前麓为天一台。篮舆直上。万千诸峰。真面呈露。奇姿秀色。一一皆可睹。尝闻前辈或有到此。以为此山不须费日穷搜。只登此台足矣。今临之信然。入寺坐歇惺楼。面势眼界甚端好。视台更胜。众香峰壁得落照逾白。如玉如雪。璀璨晶荧。环以枫林。宛然锦屏绣帐。使人目眩心醉。不知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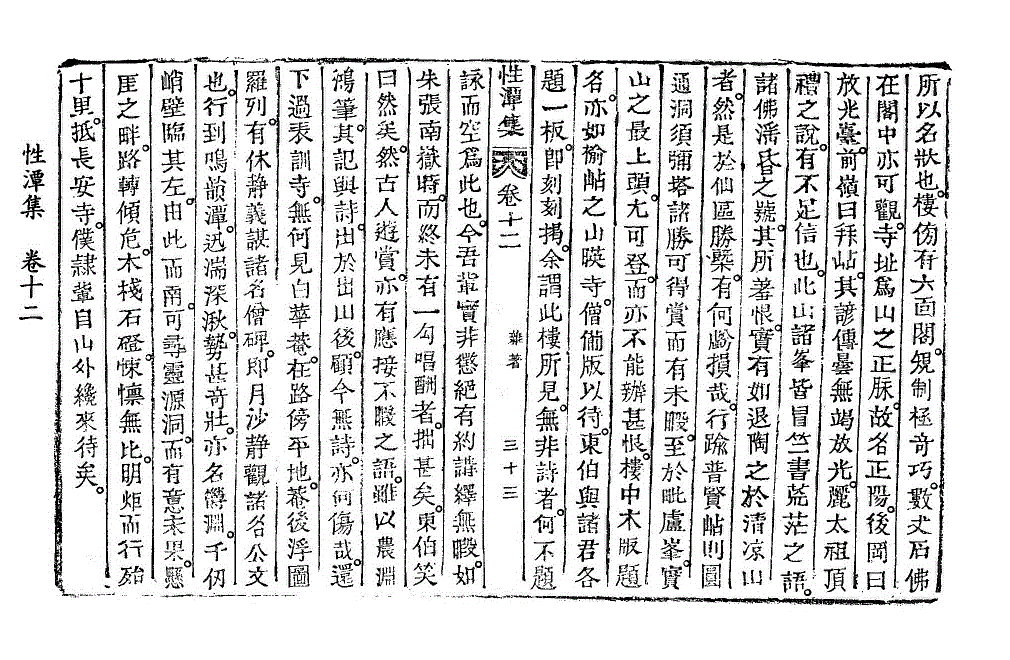 所以名状也。楼傍有六面阁。规制极奇巧。数丈石佛在阁中亦可观。寺址为山之正脉。故名正阳。后冈曰放光台。前岭曰拜岾。其谚传昙无竭放光。丽太祖顶礼之说。有不足信也。此山诸峰皆冒竺书荒茫之语。诸佛淫昏之号。其所羞恨。实有如退陶之于清凉山者。然是于仙区胜槩。有何亏损哉。行踰普贤岾则圆通洞须弥塔诸胜可得赏而有未暇。至于毗卢峰。实山之最上头。尤可登。而亦不能办甚恨。楼中木版题名。亦如榆岾之山映寺。僧备版以待。东伯与诸君各题一板。即刻刻揭。余谓此楼所见。无非诗者。何不题咏而空为此也。今吾辈实非惩绝有约讲绎无暇。如朱张南岳时。而终未有一勾唱酬者。拙甚矣。东伯笑曰然矣。然古人游赏。亦有应接不暇之语。虽以农渊鸿笔。其记与诗。出于出山后。顾今无诗。亦何伤哉。还下过表训寺。无何见白华庵。在路傍平地。庵后浮图罗列。有休静义谌诸名僧碑。即月沙静观诸名公文也。行到鸣韵潭。迅湍深湫。势甚奇壮。亦名郁渊。千仞峭壁临其左。由此而南。可寻灵源洞。而有意未果。悬厓之畔。路转倾危。木栈石磴。悚懔无比。明炬而行殆十里。抵长安寺。仆隶辈自山外才来待矣。
所以名状也。楼傍有六面阁。规制极奇巧。数丈石佛在阁中亦可观。寺址为山之正脉。故名正阳。后冈曰放光台。前岭曰拜岾。其谚传昙无竭放光。丽太祖顶礼之说。有不足信也。此山诸峰皆冒竺书荒茫之语。诸佛淫昏之号。其所羞恨。实有如退陶之于清凉山者。然是于仙区胜槩。有何亏损哉。行踰普贤岾则圆通洞须弥塔诸胜可得赏而有未暇。至于毗卢峰。实山之最上头。尤可登。而亦不能办甚恨。楼中木版题名。亦如榆岾之山映寺。僧备版以待。东伯与诸君各题一板。即刻刻揭。余谓此楼所见。无非诗者。何不题咏而空为此也。今吾辈实非惩绝有约讲绎无暇。如朱张南岳时。而终未有一勾唱酬者。拙甚矣。东伯笑曰然矣。然古人游赏。亦有应接不暇之语。虽以农渊鸿笔。其记与诗。出于出山后。顾今无诗。亦何伤哉。还下过表训寺。无何见白华庵。在路傍平地。庵后浮图罗列。有休静义谌诸名僧碑。即月沙静观诸名公文也。行到鸣韵潭。迅湍深湫。势甚奇壮。亦名郁渊。千仞峭壁临其左。由此而南。可寻灵源洞。而有意未果。悬厓之畔。路转倾危。木栈石磴。悚懔无比。明炬而行殆十里。抵长安寺。仆隶辈自山外才来待矣。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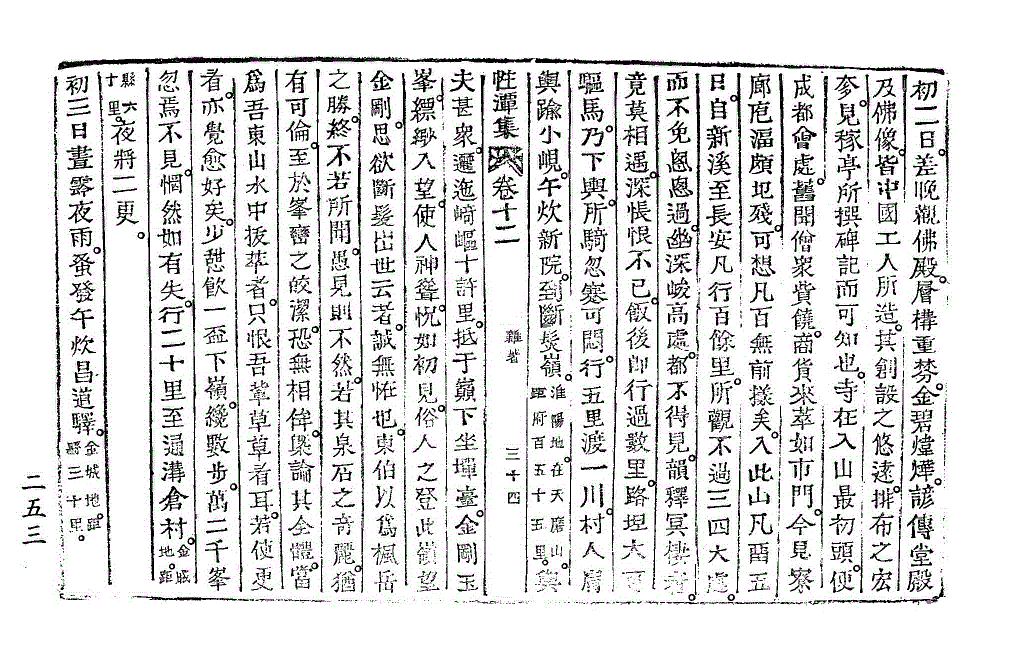 初二日。差晚观佛殿。层构重棼。金碧炜烨。谚传堂殿及佛像。皆中国工人所造。其创设之悠远。排布之宏奓。见稼亭所撰碑记而可知也。寺在入山最初头。便成都会处。旧闻僧众赀饶。商货来萃如市门。今见寮廊庖湢颇圮残。可想凡百无前㨾矣。入此山凡留五日。自新溪至长安凡行百馀里。所观不过三四大处。而不免悤悤过。幽深峻高处。都不得见。韵释冥栖者。竟莫相遇。深怅恨不已。饭后即行过数里。路坦大可驱马。乃下舆。所骑忽蹇可闷。行五里渡一川。村人肩舆踰小岘。午炊新院。到断发岭。(淮阳地。在天磨山。距府百五十五里。)舆夫甚众。逦迤崎岖十许里。抵于巅下坐墠台。金刚玉峰。缥缈入望。使人神耸。恍如初见。俗人之登此岭望金刚。思欲断发出世云者。诚无怪也。东伯以为枫岳之胜。终不若所闻。愚见则不然。若其泉石之奇丽。犹有可伦。至于峰峦之皎洁。恐无相侔。槩论其全体。当为吾东山水中拔萃者。只恨吾辈草草看耳。若使更看。亦觉愈好矣。少憩饮一杯下岭。才数步。万二千峰忽焉不见。惘然如有失。行二十里至通沟仓村。(金城地。距县六十里。)夜将二更。
初二日。差晚观佛殿。层构重棼。金碧炜烨。谚传堂殿及佛像。皆中国工人所造。其创设之悠远。排布之宏奓。见稼亭所撰碑记而可知也。寺在入山最初头。便成都会处。旧闻僧众赀饶。商货来萃如市门。今见寮廊庖湢颇圮残。可想凡百无前㨾矣。入此山凡留五日。自新溪至长安凡行百馀里。所观不过三四大处。而不免悤悤过。幽深峻高处。都不得见。韵释冥栖者。竟莫相遇。深怅恨不已。饭后即行过数里。路坦大可驱马。乃下舆。所骑忽蹇可闷。行五里渡一川。村人肩舆踰小岘。午炊新院。到断发岭。(淮阳地。在天磨山。距府百五十五里。)舆夫甚众。逦迤崎岖十许里。抵于巅下坐墠台。金刚玉峰。缥缈入望。使人神耸。恍如初见。俗人之登此岭望金刚。思欲断发出世云者。诚无怪也。东伯以为枫岳之胜。终不若所闻。愚见则不然。若其泉石之奇丽。犹有可伦。至于峰峦之皎洁。恐无相侔。槩论其全体。当为吾东山水中拔萃者。只恨吾辈草草看耳。若使更看。亦觉愈好矣。少憩饮一杯下岭。才数步。万二千峰忽焉不见。惘然如有失。行二十里至通沟仓村。(金城地。距县六十里。)夜将二更。初三日昼𩃬夜雨。蚤发午炊昌道驿。(金城地。距县三十里。)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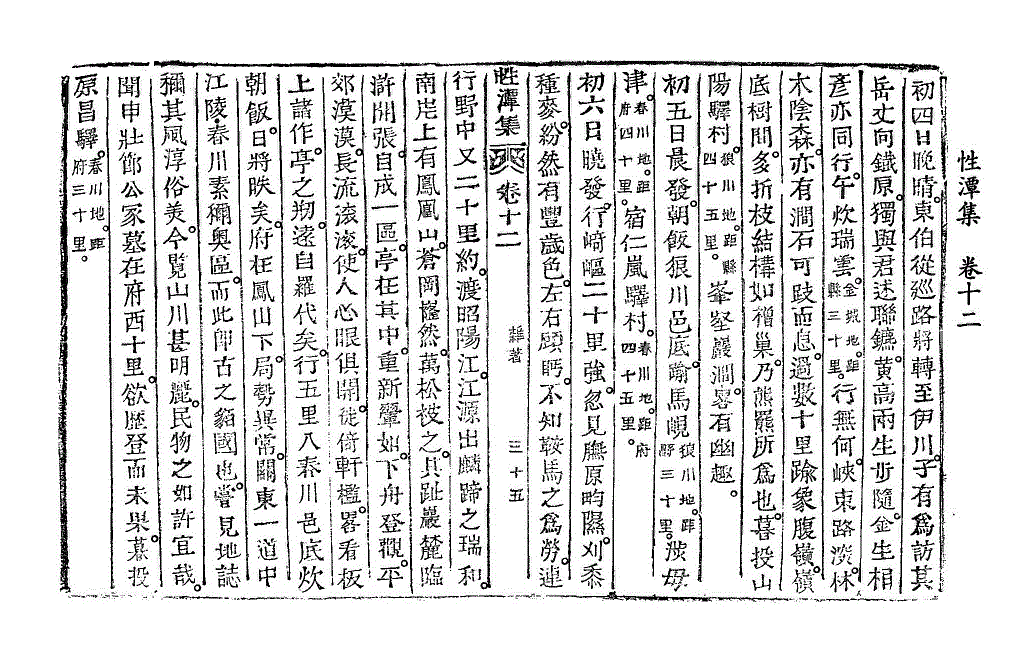 初四日晚晴。东伯从巡路将转至伊川。子有为访其岳丈向铁原。独与君述联镳。黄高两生步随。金生相彦亦同行。午炊瑞云。(金城地。距县三十里。)行无何。峡束路深。林木阴森。亦有涧石可跂而息。过数十里踰象腹岭。岭底树间。多折枝结构如橧巢。乃熊罴所为也。暮投山阳驿村。(狼川地。距县四十五里。)峰壑岩涧。略有幽趣。
初四日晚晴。东伯从巡路将转至伊川。子有为访其岳丈向铁原。独与君述联镳。黄高两生步随。金生相彦亦同行。午炊瑞云。(金城地。距县三十里。)行无何。峡束路深。林木阴森。亦有涧石可跂而息。过数十里踰象腹岭。岭底树间。多折枝结构如橧巢。乃熊罴所为也。暮投山阳驿村。(狼川地。距县四十五里。)峰壑岩涧。略有幽趣。初五日晨发。朝饭狼川邑底。踰马岘。(狼川地。距县三十里。)涉母津。(春川地。距府四十里。)宿仁岚驿村。(春川地。距府四十五里。)
初六日晓发。行崎岖二十里强。忽见膴原畇隰。刈黍种麦。纷然有丰岁色。左右顾眄。不知鞍马之为劳。连行野中又二十里约。渡昭阳江。江源出麟蹄之瑞和。南岸上有凤凰山。苍冈隆然。万松被之。其趾岩麓临浒开张。自成一区。亭在其中。重新翚如。下舟登观。平郊漠漠。长流滚滚。使人心眼俱开。徙倚轩槛。略看板上诸作。亭之刱。远自罗代矣。行五里入春川邑底炊朝饭。日将昳矣。府在凤山下。局势异常。关东一道中江陵,春川素称奥区。而此即古之貊国也。尝见地志称其风淳俗美。今览山川甚明丽。民物之如许宜哉。闻申壮节公冢墓在府西十里。欲历登而未果。暮投原昌驿。(春川地。距府三十里。)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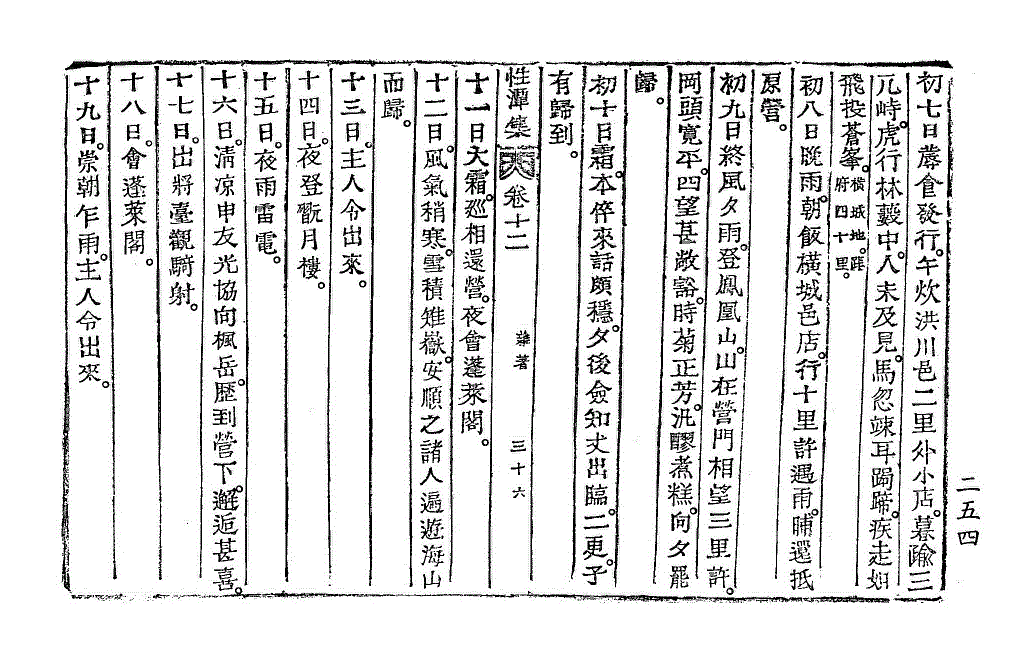 初七日蓐食发行。午炊洪川邑二里外小店。暮踰三兀峙。虎行林薮中。人未及见。马忽竦耳跼蹄。疾走如飞投苍峰。(横城地。距府四十里。)
初七日蓐食发行。午炊洪川邑二里外小店。暮踰三兀峙。虎行林薮中。人未及见。马忽竦耳跼蹄。疾走如飞投苍峰。(横城地。距府四十里。)初八日晚雨。朝饭横城邑店。行十里许遇雨。晡还抵原营。
初九日终风夕雨。登凤凰山。山在营门相望三里许。冈头宽平。四望甚敞豁。时菊正芳。汎醪煮糕。向夕罢归。
初十日霜。本倅来话颇稳。夕后佥知丈出临。二更。子有归到。
十一日大霜。巡相还营。夜会蓬莱阁。
十二日。风气稍寒。雪积雉岳。安顺之诸人遍游海山而归。
十三日。主人令出来。
十四日。夜登玩月楼。
十五日。夜雨雷电。
十六日。清凉申友光协向枫岳。历到营下。邂逅甚喜。
十七日。出将台观骑射。
十八日。会蓬莱阁。
十九日。崇朝乍雨。主人令出来。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5H 页
 二十日。往龟石亭。岩石如龟形临水奇胜。
二十日。往龟石亭。岩石如龟形临水奇胜。二十一日乍阴。与黄生晚发。宿文幕店。
二十二日霜。早发朝饭兴原仓村。暮入长厚院郑戚家。郑君禹锡有所叩质。殊可喜。
二十三日晚发。艰到法村。
二十四日晏发。暂秣镇川邑店。暮抵凤岩。蔡进士奎燮,商燮诸友会话至夜分。
二十五日早发。午炊胜川店。暮入金谷。
二十六日。朝雨夜雪。
二十七日。雨雪且风。
二十八日发归。秣马德坪。暮抵葛吉。
二十九日早发。午炊马浦。薄曛到家。
枫岳之游。非不遂夙愿。而尚恨未穷探。虽欲更见而不可得。其所憧憧者。最在毗卢上矣。翌年季秋。东伯有书。以为枫山再见则果绝胜于昨秋。渊翁所谓再见胜于始见者。诚得山水之趣矣。况灵源洞须弥塔。昨秋之所未见。而今行则见之。又上毗卢绝顶则尤庵先生题名。宛然如昨日矣。用我沧洲先祖卢峰韵吟一绝曰。能使华阳夫子来。万千峰上独崔嵬。岩苔不蚀题名字。岁月仙山问几回。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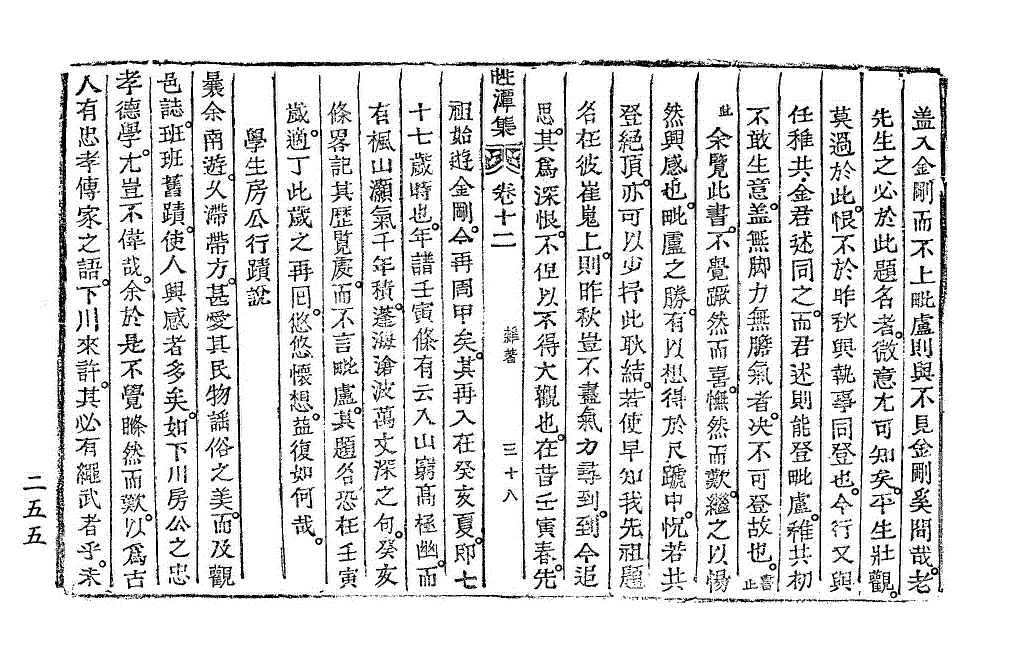 盖入金刚而不上毗卢则与不见金刚奚间哉。老先生之必于此题名者。微意尤可知矣。平生壮观。莫过于此。恨不于昨秋与执事同登也。今行又与任稚共,金君述同之。而君述则能登毗卢。稚共初不敢生意。盖无脚力无胆气者。决不可登故也。(书止此。)余览此书。不觉蹶然而喜。怃然而叹。继之以惕然兴感也。毗卢之胜。有以想得于尺蹄中。恍若共登绝顶。亦可以少抒此耿结。若使早知我先祖题名在彼崔嵬上。则昨秋岂不尽气力寻到。到今追思。其为深恨。不但以不得大观也。在昔壬寅春。先祖始游金刚。今再周甲矣。其再入在癸亥夏。即七十七岁时也。年谱壬寅条有云入山穷高极幽。而有枫山灏气千年积。蓬海沧波万丈深之句。癸亥条略记其历览处。而不言毗卢。其题名恐在壬寅岁。适丁此岁之再回。悠悠怀想。益复如何哉。
盖入金刚而不上毗卢则与不见金刚奚间哉。老先生之必于此题名者。微意尤可知矣。平生壮观。莫过于此。恨不于昨秋与执事同登也。今行又与任稚共,金君述同之。而君述则能登毗卢。稚共初不敢生意。盖无脚力无胆气者。决不可登故也。(书止此。)余览此书。不觉蹶然而喜。怃然而叹。继之以惕然兴感也。毗卢之胜。有以想得于尺蹄中。恍若共登绝顶。亦可以少抒此耿结。若使早知我先祖题名在彼崔嵬上。则昨秋岂不尽气力寻到。到今追思。其为深恨。不但以不得大观也。在昔壬寅春。先祖始游金刚。今再周甲矣。其再入在癸亥夏。即七十七岁时也。年谱壬寅条有云入山穷高极幽。而有枫山灏气千年积。蓬海沧波万丈深之句。癸亥条略记其历览处。而不言毗卢。其题名恐在壬寅岁。适丁此岁之再回。悠悠怀想。益复如何哉。学生房公行迹说
曩余南游。久滞带方。甚爱其民物谣俗之美。而及观邑志。班班旧迹。使人兴感者多矣。如下川房公之忠孝德学。尤岂不伟哉。余于是不觉𥉉然而叹。以为古人有忠孝传家之语。下川来许。其必有绳武者乎。未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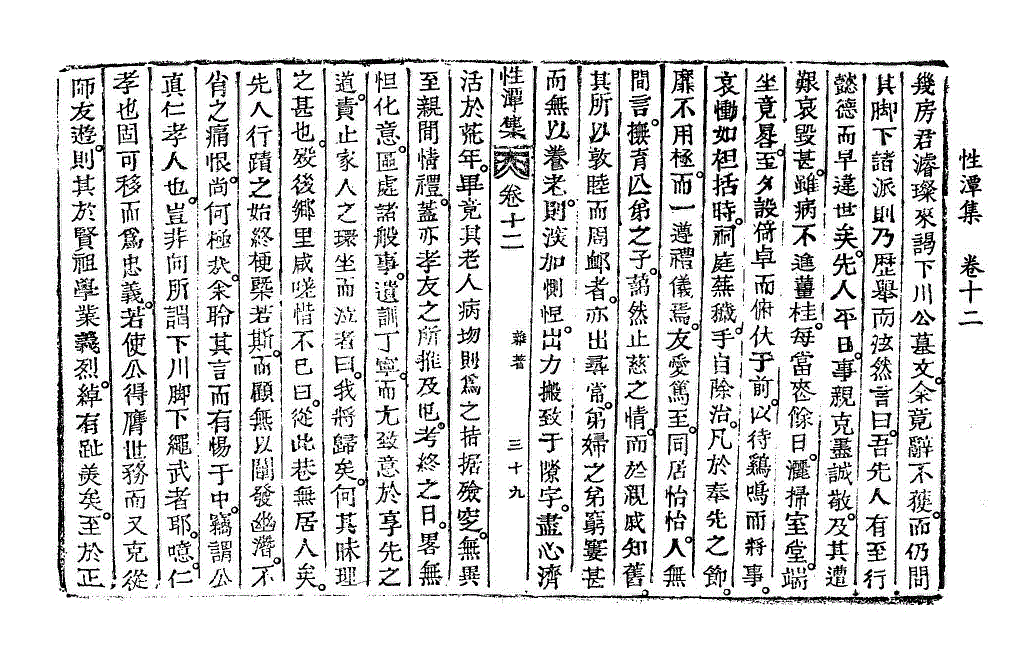 几房君浚璨来谒下川公墓文。余竟辞不获。而仍问其脚下诸派则乃历举而泫然言曰。吾先人有至行懿德而早违世矣。先人平日。事亲克尽诚敬。及其遭艰哀毁甚。虽病不进姜桂。每当丧馀日。洒扫室堂。端坐竟晷。至夕设倚卓而俯伏于前。以待鸡鸣而将事。哀恸如袒括时。祠庭芜秽。手自除治。凡于奉先之节。靡不用极。而一遵礼仪焉。友爱笃至。同居怡怡。人无间言。抚育亡弟之子。蔼然止慈之情。而于亲戚知旧。其所以敦睦而周恤者。亦出寻常。弟妇之弟穷窭甚而无以养老。则深加恻怛。出力搬致于隙宇。尽心济活于荒年。毕竟其老人病殁则为之拮据殓窆。无异至亲间情礼。盖亦孝友之所推及也。考终之日。略无怛化意。区处诸般事。遗训丁宁。而尤致意于享先之道。责止家人之环坐而泣者曰。我将归矣。何其昧理之甚也。殁后乡里咸嗟惜不已曰。从此巷无居人矣。先人行迹之始终梗槩若斯。而顾无以阐发幽潜。不肖之痛恨。尚何极哉。余聆其言而有惕于中。窃谓公真仁孝人也。岂非向所谓下川脚下绳武者耶。噫。仁孝也固可移而为忠义。若使公得膺世务而又克从师友游。则其于贤祖学业义烈。绰有趾美矣。至于正
几房君浚璨来谒下川公墓文。余竟辞不获。而仍问其脚下诸派则乃历举而泫然言曰。吾先人有至行懿德而早违世矣。先人平日。事亲克尽诚敬。及其遭艰哀毁甚。虽病不进姜桂。每当丧馀日。洒扫室堂。端坐竟晷。至夕设倚卓而俯伏于前。以待鸡鸣而将事。哀恸如袒括时。祠庭芜秽。手自除治。凡于奉先之节。靡不用极。而一遵礼仪焉。友爱笃至。同居怡怡。人无间言。抚育亡弟之子。蔼然止慈之情。而于亲戚知旧。其所以敦睦而周恤者。亦出寻常。弟妇之弟穷窭甚而无以养老。则深加恻怛。出力搬致于隙宇。尽心济活于荒年。毕竟其老人病殁则为之拮据殓窆。无异至亲间情礼。盖亦孝友之所推及也。考终之日。略无怛化意。区处诸般事。遗训丁宁。而尤致意于享先之道。责止家人之环坐而泣者曰。我将归矣。何其昧理之甚也。殁后乡里咸嗟惜不已曰。从此巷无居人矣。先人行迹之始终梗槩若斯。而顾无以阐发幽潜。不肖之痛恨。尚何极哉。余聆其言而有惕于中。窃谓公真仁孝人也。岂非向所谓下川脚下绳武者耶。噫。仁孝也固可移而为忠义。若使公得膺世务而又克从师友游。则其于贤祖学业义烈。绰有趾美矣。至于正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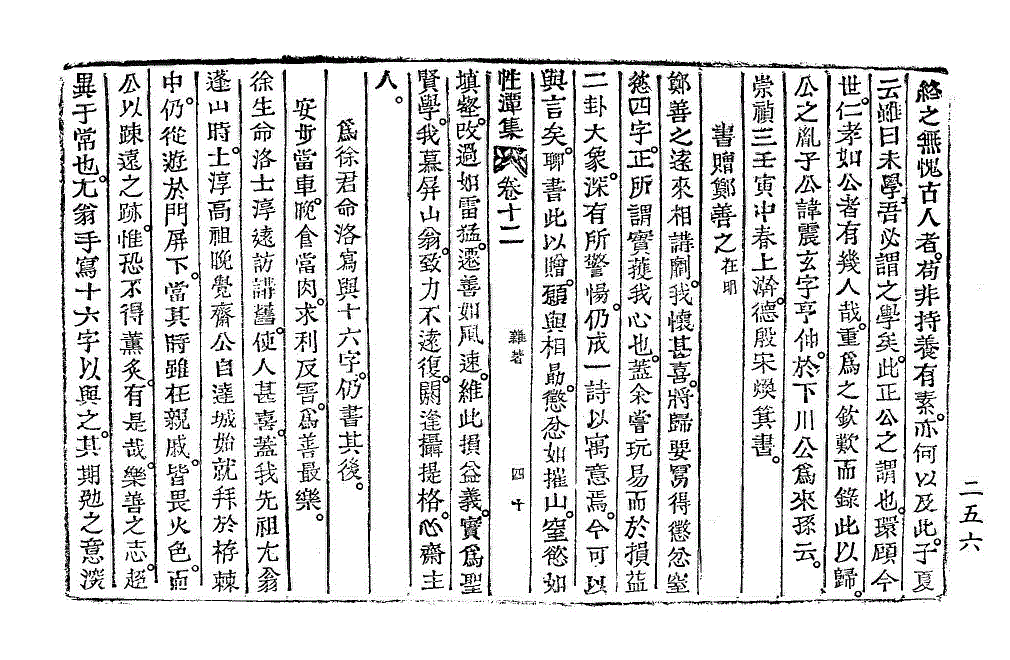 终之无愧古人者。苟非持养有素。亦何以及此。子夏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正公之谓也。环顾今世。仁孝如公者有几人哉。重为之钦叹而录此以归。公之胤子公讳震玄字亨仲。于下川公为来孙云。 崇祯三壬寅中春上浣。德殷宋焕箕书。
终之无愧古人者。苟非持养有素。亦何以及此。子夏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正公之谓也。环顾今世。仁孝如公者有几人哉。重为之钦叹而录此以归。公之胤子公讳震玄字亨仲。于下川公为来孙云。 崇祯三壬寅中春上浣。德殷宋焕箕书。书赠郑善之(在明)
郑善之远来相讲劘。我怀甚喜。将归要写得惩忿窒欲四字。正所谓实获我心也。盖余尝玩易而于损益二卦大象。深有所警惕。仍成一诗以寓意焉。今可以与言矣。聊书此以赠。愿与相勖。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改过如雷猛。迁善如风速。维此损益义。实为圣贤学。我慕屏山翁。致力不远复。阏逢摄提格。心斋主人。
为徐君命洛写与十六字。仍书其后。
安步当车。晚食当肉。求利反害。为善最乐。
徐生命洛士淳远访讲旧。使人甚喜。盖我先祖尤翁蓬山时。士淳高祖晚觉斋公自达城始就拜于栫棘中。仍从游于门屏下。当其时虽在亲戚。皆畏火色。而公以疏远之迹。惟恐不得薰炙。有是哉。乐善之志。超异于常也。尤翁手写十六字以与之。其期勉之意深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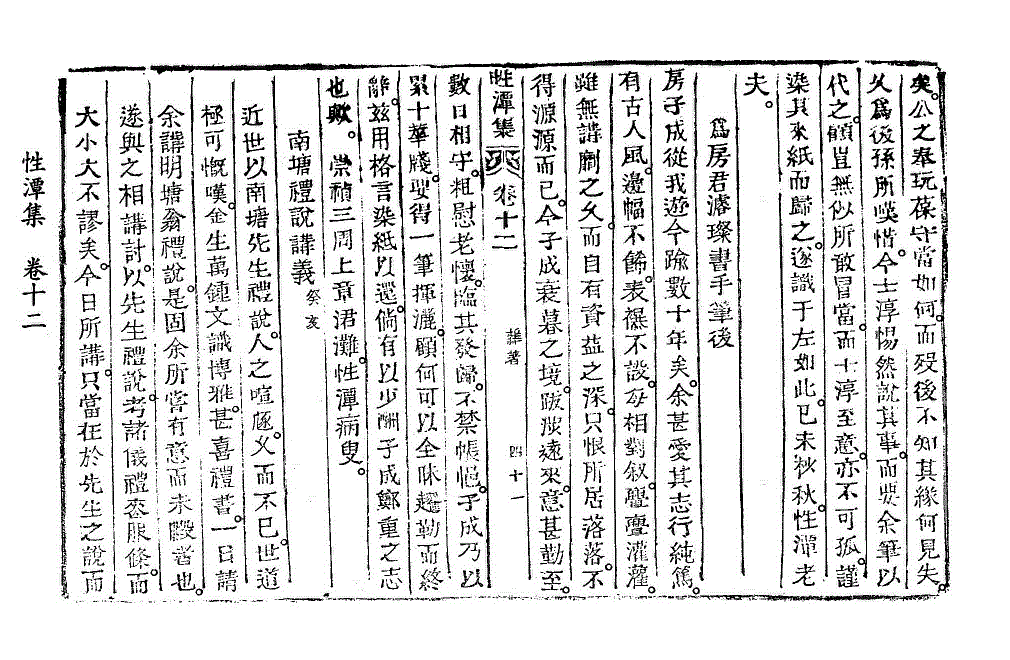 矣。公之奉玩葆守当如何。而殁后不知其缘何见失。久为后孙所叹惜。今士淳惕然说其事。而要余笔以代之。顾岂无似所敢冒当。而士淳至意。亦不可孤。谨染其来纸而归之。遂识于左如此。已未杪秋。性潭老夫。
矣。公之奉玩葆守当如何。而殁后不知其缘何见失。久为后孙所叹惜。今士淳惕然说其事。而要余笔以代之。顾岂无似所敢冒当。而士淳至意。亦不可孤。谨染其来纸而归之。遂识于左如此。已未杪秋。性潭老夫。为房君浚璨书手笔后
房子成从我游今踰数十年矣。余甚爱其志行纯笃。有古人风。边幅不饰。表襮不设。每相对叙。亹亹灌灌。虽无讲劘之久。而自有资益之深。只恨所居落落。不得源源而已。今子成衰暮之境。跋涉远来。意甚勤至。数日相守。粗慰老怀。临其发归。不禁帐(一作怅)悒。子成乃以累十华笺。要得一笔挥洒。顾何可以全昧趯勒而终辞。玆用格言染纸以还。倘有以少酬子成郑重之志也欤。 崇祯三周上章涒滩。性潭病叟。
南塘礼说讲义(癸亥)
近世以南塘先生礼说。人之喧豗。久而不已。世道极可慨叹。金生万钟文识博雅。甚喜礼书。一日请余讲明塘翁礼说。是固余所尝有意而未暇者也。遂与之相讲讨。以先生礼说。考诸仪礼丧服条。而大小大不谬矣。今日所讲。只当在于先生之说而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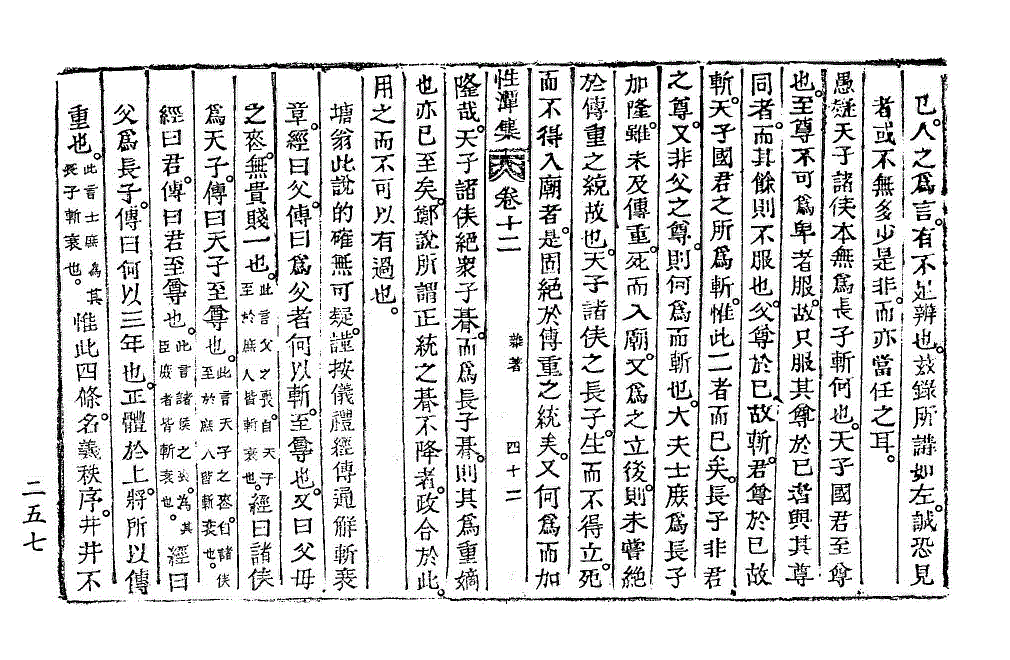 已。人之为言。有不足辨也。玆录所讲如左。诚恐见者或不无多少是非。而亦当任之耳。
已。人之为言。有不足辨也。玆录所讲如左。诚恐见者或不无多少是非。而亦当任之耳。愚疑天子诸侯本无为长子斩何也。天子国君至尊也。至尊不可为卑者服。故只服其尊于己者与其尊同者。而其馀则不服也。父尊于己故斩。君尊于己故斩。天子国君之所为斩。惟此二者而已矣。长子非君之尊。又非父之尊。则何为而斩也。大夫士庶为长子加隆。虽未及传重。死而入庙。又为之立后。则未尝绝于传重之统故也。天子诸侯之长子。生而不得立。死而不得入庙者。是固绝于传重之统矣。又何为而加隆哉。天子诸侯绝众子期。而为长子期。则其为重嫡也亦已至矣。郑说所谓正统之期不降者。政合于此。用之而不可以有过也。
塘翁此说的确无可疑。谨按仪礼经传通解斩衰章。经曰父。传曰为父者何以斩。至尊也。又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此言父之丧。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斩衰也。)经曰诸侯为天子。传曰天子至尊也。(此言天子之丧。自诸侯至于庶人皆斩衰也。)经曰君。传曰君至尊也。(此言诸侯之丧。为其臣庶者皆斩衰也。)经曰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将所以传重也。(此言士庶为其长子斩衰也。)惟此四条。名义秩序。井井不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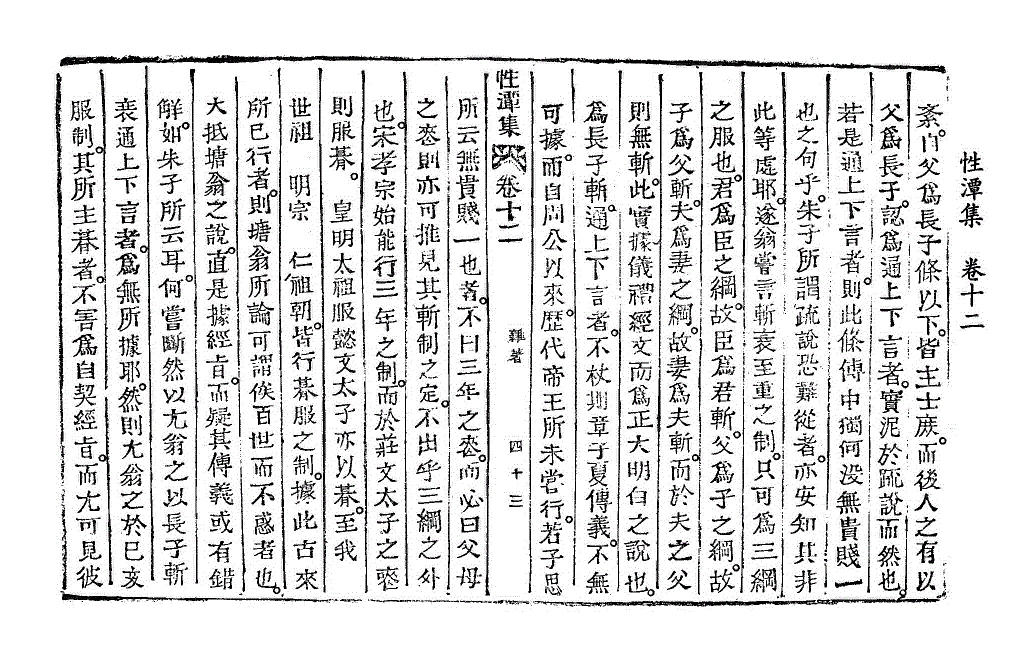 紊。自父为长子条以下。皆主士庶。而后人之有以父为长子。认为通上下言者。实泥于疏说而然也。若是通上下言者。则此条传中独何没无贵贱一也之句乎。朱子所谓疏说恐难从者。亦安知其非此等处耶。遂翁尝言斩衰至重之制。只可为三纲之服也。君为臣之纲。故臣为君斩。父为子之纲。故子为父斩。夫为妻之纲。故妻为夫斩。而于夫之父则无斩。此实据仪礼经文而为正大明白之说也。为长子斩。通上下言者。不杖期章子夏传义。不无可据。而自周公以来。历代帝王所未尝行。若子思所云无贵贱一也者。不曰三年之丧。而必曰父母之丧则亦可推见其斩制之定。不出乎三纲之外也。宋孝宗始能行三年之制。而于庄文太子之丧则服期。 皇明太祖服懿文太子亦以期。至我 世祖 明宗 仁祖朝。皆行期服之制。据此古来所已行者。则塘翁所论可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大抵塘翁之说。直是据经旨。而疑其传义或有错解。如朱子所云耳。何尝断然以尤翁之以长子斩衰通上下言者。为无所据耶。然则尤翁之于己亥服制。其所主期者。不害为自契经旨。而尤可见彼
紊。自父为长子条以下。皆主士庶。而后人之有以父为长子。认为通上下言者。实泥于疏说而然也。若是通上下言者。则此条传中独何没无贵贱一也之句乎。朱子所谓疏说恐难从者。亦安知其非此等处耶。遂翁尝言斩衰至重之制。只可为三纲之服也。君为臣之纲。故臣为君斩。父为子之纲。故子为父斩。夫为妻之纲。故妻为夫斩。而于夫之父则无斩。此实据仪礼经文而为正大明白之说也。为长子斩。通上下言者。不杖期章子夏传义。不无可据。而自周公以来。历代帝王所未尝行。若子思所云无贵贱一也者。不曰三年之丧。而必曰父母之丧则亦可推见其斩制之定。不出乎三纲之外也。宋孝宗始能行三年之制。而于庄文太子之丧则服期。 皇明太祖服懿文太子亦以期。至我 世祖 明宗 仁祖朝。皆行期服之制。据此古来所已行者。则塘翁所论可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大抵塘翁之说。直是据经旨。而疑其传义或有错解。如朱子所云耳。何尝断然以尤翁之以长子斩衰通上下言者。为无所据耶。然则尤翁之于己亥服制。其所主期者。不害为自契经旨。而尤可见彼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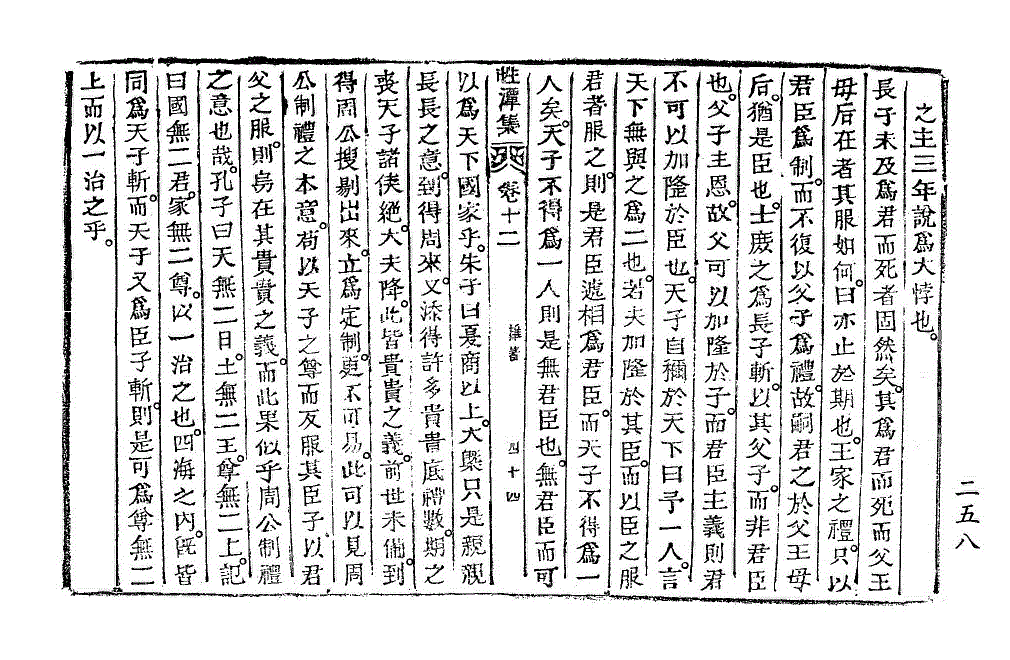 之主三年说为大悖也。
之主三年说为大悖也。长子未及为君而死者固然矣。其为君而死而父王母后在者其服如何。曰亦止于期也。王家之礼。只以君臣为制。而不复以父子为礼。故嗣君之于父王母后。犹是臣也。士庶之为长子斩。以其父子。而非君臣也。父子主恩。故父可以加隆于子。而君臣主义则君不可以加隆于臣也。天子自称于天下曰予一人。言天下无与之为二也。若夫加隆于其臣。而以臣之服君者服之。则是君臣递相为君臣。而天子不得为一人矣。天子不得为一人则是无君臣也。无君臣而可以为天下国家乎。朱子曰夏商以上。大槩只是亲亲长长之意。到得周来。又添得许多贵贵底礼数。期之丧天子诸侯绝。大夫降。此皆贵贵之义。前世未备。到得周公搜剔出来。立为定制。更不可易。此可以见周公制礼之本意。苟以天子之尊而反服其臣子以君父之服。则乌在其贵贵之义。而此果似乎周公制礼之意也哉。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尊无二上。记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四海之内。既皆同为天子斩。而天子又为臣子斩。则是可为尊无二上而以一治之乎。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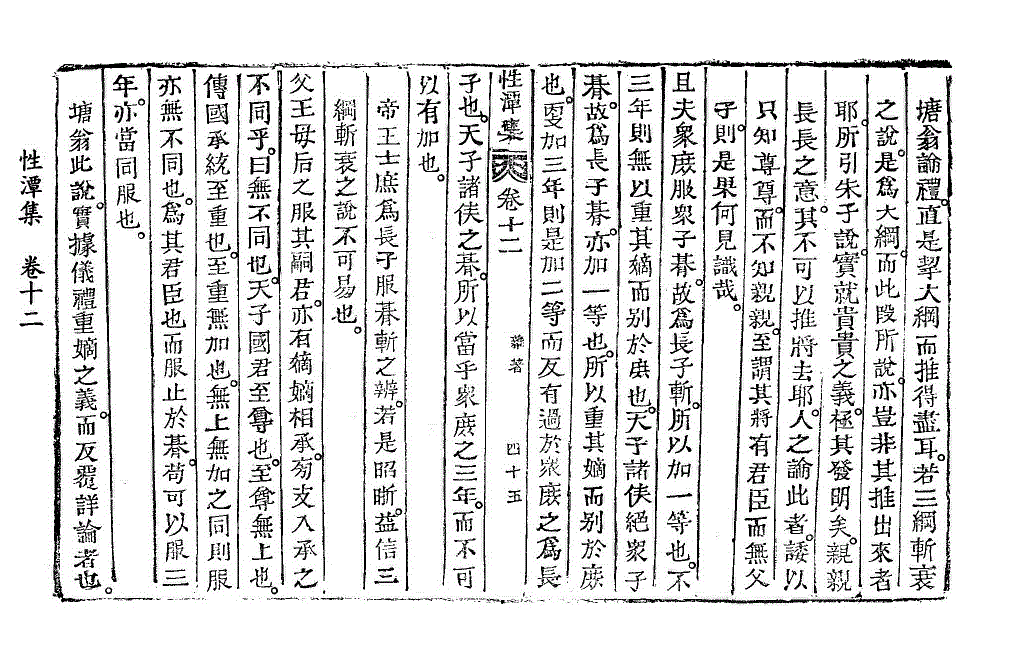 塘翁论礼。直是挈大纲而推得尽耳。若三纲斩衰之说。是为大纲。而此段所说。亦岂非其推出来者耶。所引朱子说。实就贵贵之义。极其发明矣。亲亲长长之意。其不可以推将去耶。人之论此者。诿以只知尊尊。而不知亲亲。至谓其将有君臣而无父子。则是果何见识哉。
塘翁论礼。直是挈大纲而推得尽耳。若三纲斩衰之说。是为大纲。而此段所说。亦岂非其推出来者耶。所引朱子说。实就贵贵之义。极其发明矣。亲亲长长之意。其不可以推将去耶。人之论此者。诿以只知尊尊。而不知亲亲。至谓其将有君臣而无父子。则是果何见识哉。且夫众庶服众子期。故为长子斩。所以加一等也。不三年则无以重其嫡而别于庶也。天子诸侯绝众子期。故为长子期。亦加一等也。所以重其嫡而别于庶也。更加三年则是加二等而反有过于众庶之为长子也。天子诸侯之期。所以当乎众庶之三年。而不可以有加也。
帝王士庶为长子服期斩之辨。若是昭晢。益信三纲斩衰之说不可易也。
父王母后之服其嗣君。亦有嫡嫡相承。旁支入承之不同乎。曰无不同也。天子国君至尊也。至尊无上也。传国承统至重也。至重无加也。无上无加之同则服亦无不同也。为其君臣也而服止于期。苟可以服三年。亦当同服也。
塘翁此说。实据仪礼重嫡之义。而反覆详论者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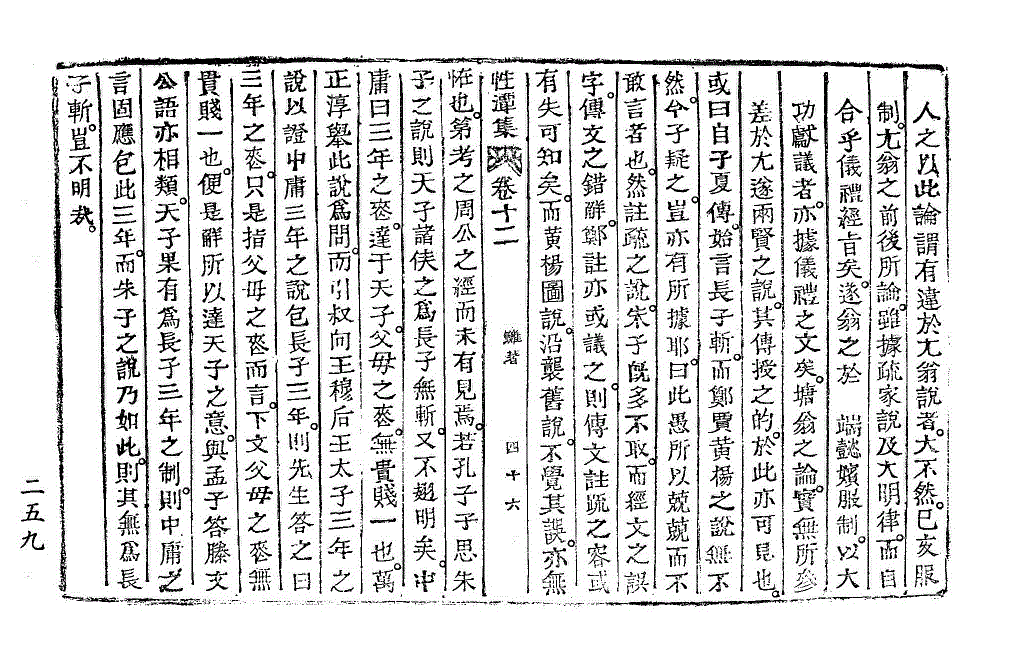 人之以此论谓有违于尤翁说者。大不然。己亥服制。尤翁之前后所论。虽据疏家说及大明律。而自合乎仪礼经旨矣。遂翁之于 端懿嫔服制。以大功献议者。亦据仪礼之文矣。塘翁之论。实无所参差于尤遂两贤之说。其传授之的。于此亦可见也。
人之以此论谓有违于尤翁说者。大不然。己亥服制。尤翁之前后所论。虽据疏家说及大明律。而自合乎仪礼经旨矣。遂翁之于 端懿嫔服制。以大功献议者。亦据仪礼之文矣。塘翁之论。实无所参差于尤遂两贤之说。其传授之的。于此亦可见也。或曰自子夏传。始言长子斩。而郑贾黄杨之说无不然。今子疑之。岂亦有所据耶。曰此愚所以兢兢而不敢言者也。然注疏之说。朱子既多不取。而经文之误字。传文之错解。郑注亦或议之。则传文注疏之容或有失可知矣。而黄杨图说。沿袭旧说。不觉其误。亦无怪也。第考之周公之经而未有见焉。若孔子子思朱子之说则天子诸侯之为长子无斩。又不翅明矣。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万正淳举此说为问。而引叔向王穆后王太子三年之说以證中庸三年之说包长子三年。则先生答之曰三年之丧。只是指父母之丧而言。下文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便是解所以达天子之意。与孟子答滕文公语亦相类。天子果有为长子三年之制。则中庸之言固应包此三年。而朱子之说乃如此。则其无为长子斩。岂不明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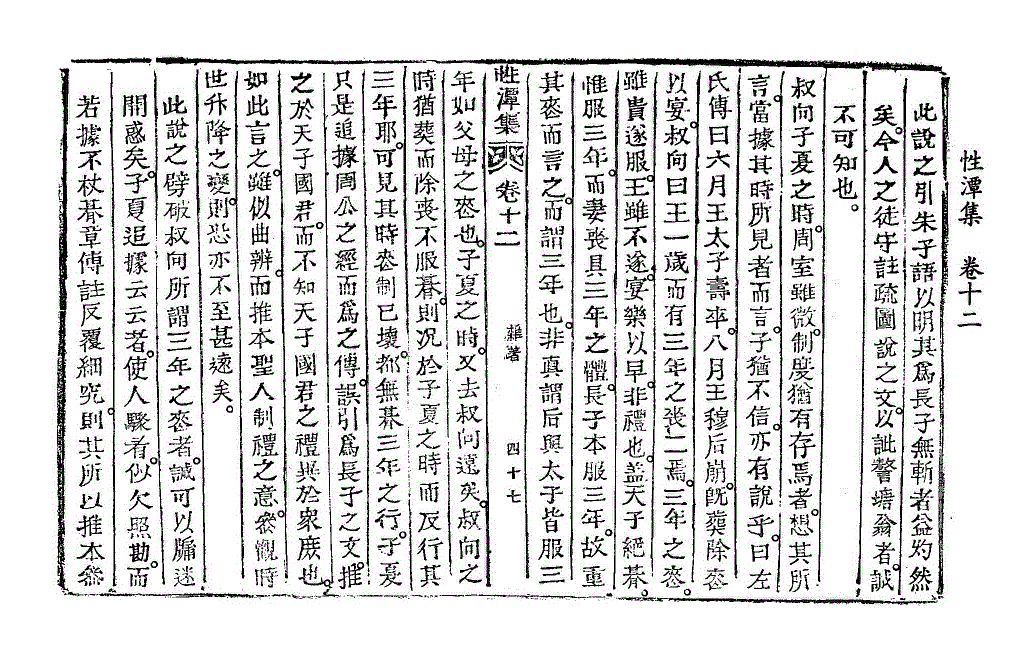 此说之引朱子语以明其为长子无斩者益灼然矣。今人之徒守注疏图说之文。以訾謷塘翁者。诚不可知也。
此说之引朱子语以明其为长子无斩者益灼然矣。今人之徒守注疏图说之文。以訾謷塘翁者。诚不可知也。叔向子夏之时。周室虽微。制度犹有存焉者。想其所言。当据其时所见者而言。子犹不信。亦有说乎。曰左氏传曰六月王太子寿卒。八月王穆后崩。既葬除丧以宴。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王虽不遂。宴乐以早。非礼也。盖天子绝期。惟服三年。而妻丧具三年之体。长子本服三年。故重其丧而言之。而谓三年也。非真谓后与太子皆服三年如父母之丧也。子夏之时。又去叔向远矣。叔向之时犹葬而除丧不服期。则况于子夏之时而反行其三年耶。可见其时丧制已坏。都无期三年之行。子夏只是追据周公之经而为之传。误引为长子之文。推之于天子国君。而不知天子国君之礼异于众庶也。如此言之。虽似曲辨。而推本圣人制礼之意。参观时世升降之变。则恐亦不至甚远矣。
此说之劈破叔向所谓三年之丧者。诚可以牖迷开惑矣。子夏追据云云者。使人骤看。似欠照勘。而若据不杖期章传注反覆细究。则其所以推本参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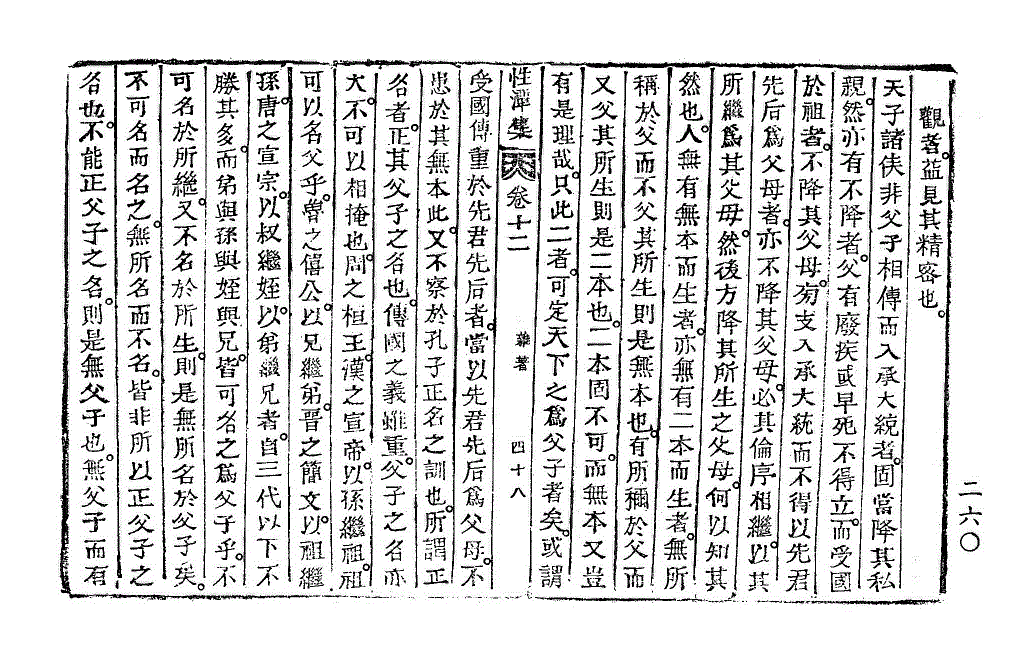 观者。益见其精密也。
观者。益见其精密也。天子诸侯非父子相传而入承大统者。固当降其私亲。然亦有不降者。父有废疾或早死不得立。而受国于祖者。不降其父母。旁支入承大统而不得以先君先后为父母者。亦不降其父母。必其伦序相继。以其所继为其父母。然后方降其所生之父母。何以知其然也。人无有无本而生者。亦无有二本而生者。无所称于父而不父其所生则是无本也。有所称于父而又父其所生则是二本也。二本固不可。而无本又岂有是理哉。只此二者。可定天下之为父子者矣。或谓受国传重于先君先后者。当以先君先后为父母。不患于其无本此。又不察于孔子正名之训也。所谓正名者。正其父子之名也。传国之义虽重。父子之名亦大。不可以相掩也。周之桓王。汉之宣帝。以孙继祖。祖可以名父乎。鲁之僖公。以兄继弟。晋之简文。以祖继孙。唐之宣宗。以叔继侄。以弟继兄者。自三代以下不胜其多。而弟与孙与侄与兄。皆可名之为父子乎。不可名于所继。又不名于所生。则是无所名于父子矣。不可名而名之。无所名而不名。皆非所以正父子之名也。不能正父子之名。则是无父子也。无父子而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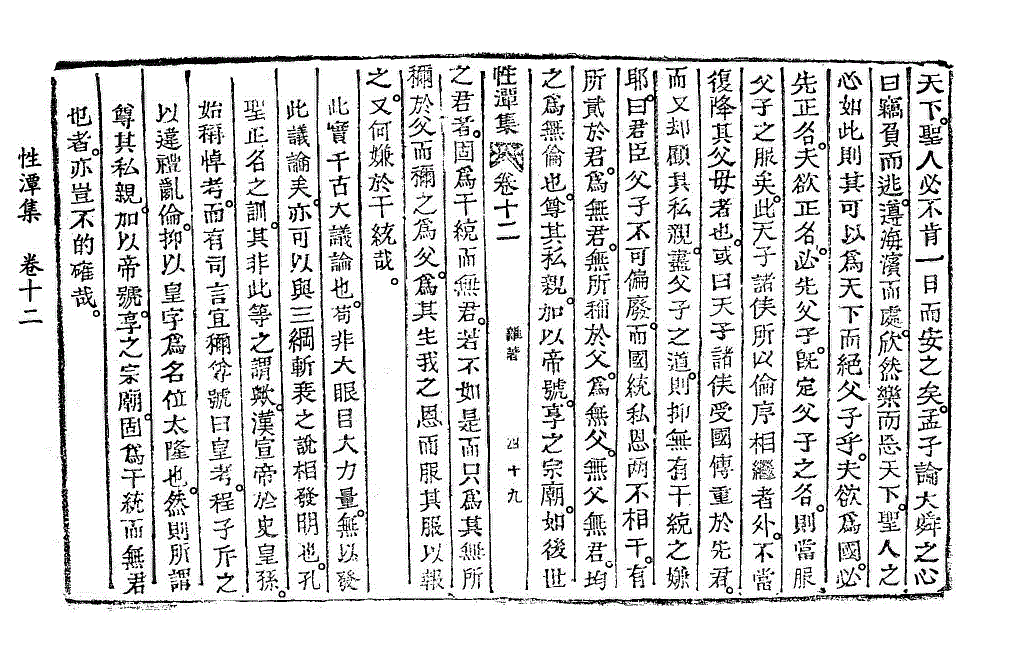 天下。圣人必不肯一日而安之矣。孟子论大舜之心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欣然乐而忘天下。圣人之心如此则其可以为天下而绝父子乎。夫欲为国。必先正名。夫欲正名。必先父子。既定父子之名。则当服父子之服矣。此天子诸侯所以伦序相继者外。不当复降其父母者也。或曰天子诸侯受国传重于先君。而又却顾其私亲。尽父子之道。则抑无有干统之嫌耶。曰君臣父子不可偏废。而国统私恩两不相干。有所贰于君。为无君。无所称于父。为无父。无父无君。均之为无伦也。尊其私亲。加以帝号。享之宗庙。如后世之君者。固为干统而无君。若不如是而只为其无所称于父而称之为父。为其生我之恩而服其服以报之。又何嫌于干统哉。
天下。圣人必不肯一日而安之矣。孟子论大舜之心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欣然乐而忘天下。圣人之心如此则其可以为天下而绝父子乎。夫欲为国。必先正名。夫欲正名。必先父子。既定父子之名。则当服父子之服矣。此天子诸侯所以伦序相继者外。不当复降其父母者也。或曰天子诸侯受国传重于先君。而又却顾其私亲。尽父子之道。则抑无有干统之嫌耶。曰君臣父子不可偏废。而国统私恩两不相干。有所贰于君。为无君。无所称于父。为无父。无父无君。均之为无伦也。尊其私亲。加以帝号。享之宗庙。如后世之君者。固为干统而无君。若不如是而只为其无所称于父而称之为父。为其生我之恩而服其服以报之。又何嫌于干统哉。此实千古大议论也。苟非大眼目大力量。无以发此议论矣。亦可以与三纲斩衰之说相发明也。孔圣正名之训。其非此等之谓欤。汉宣帝于史皇孙。始称悼考。而有司言宜称尊号曰皇考。程子斥之以违礼乱伦。抑以皇字为名位太隆也。然则所谓尊其私亲。加以帝号。享之宗庙。固为干统而无君也者。亦岂不的确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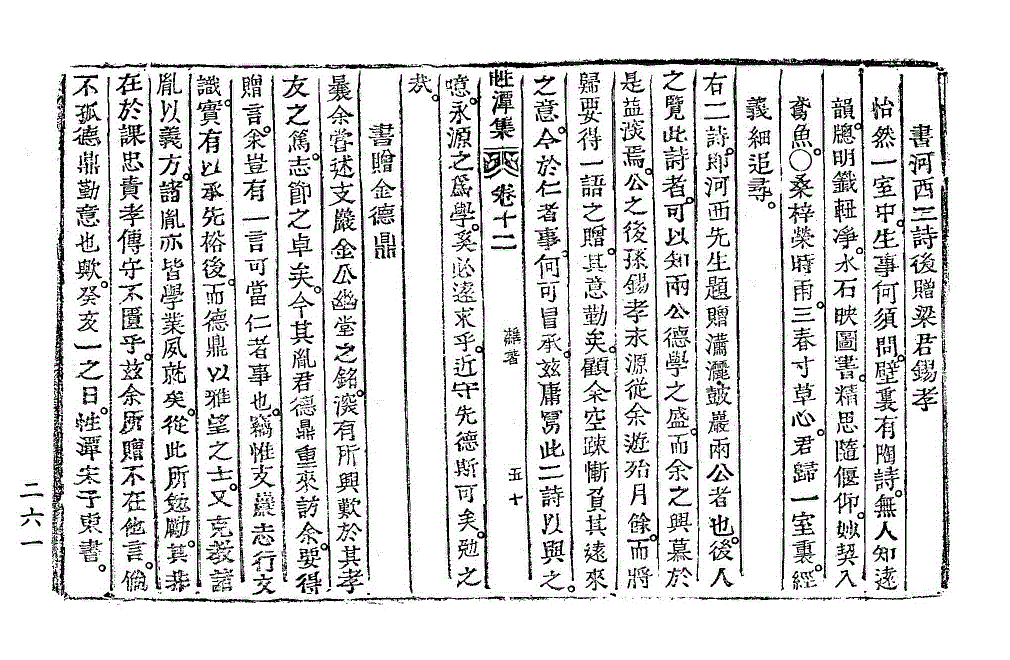 书河西二诗后赠梁君锡孝
书河西二诗后赠梁君锡孝怡然一室中。生事何须问。壁里有陶诗。无人知远韵。窗明签轴净。水石映图书。精思随偃仰。妙契入鸢鱼。○桑梓荣时雨。三春寸草心。君归一室里。经义细追寻。
右二诗。即河西先生题赠潇洒,鼓岩两公者也。后人之览此诗者。可以知两公德学之盛。而余之兴慕于是益深焉。公之后孙锡孝永源从余游殆月馀。而将归要得一语之赠。其意勤矣。顾余空疏惭负其远来之意。今于仁者事。何可冒承。玆庸写此二诗以与之。噫。永源之为学。奚必远求乎。近守先德斯可矣。勉之哉。
书赠金德鼎
曩余尝述支岩金公幽堂之铭。深有所兴叹于其孝友之笃。志节之卓矣。今其胤君德鼎重来访余。要得赠言。余岂有一言可当仁者事也。窃惟支岩志行文识。实有以承先裕后。而德鼎以雅望之士。又克教诸胤以义方。诸胤亦皆学业夙就矣。从此所勉励。其非在于课忠责孝传守不匮乎。玆余所赠不在他言。倘不孤德鼎勤意也欤。癸亥一之日。性潭宋子东书。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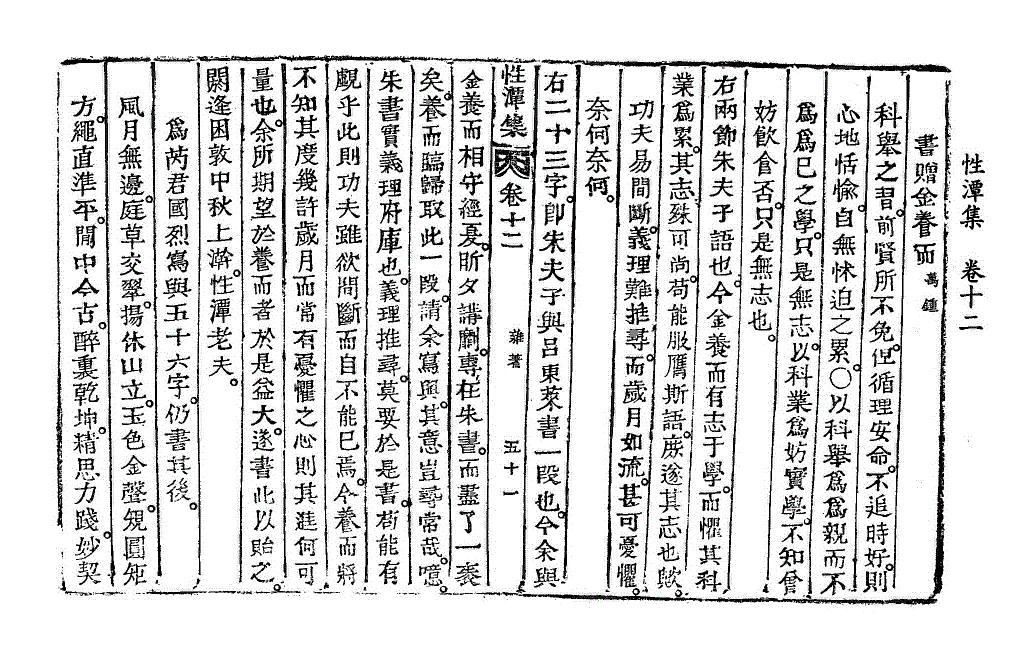 书赠金养而(万钟)
书赠金养而(万钟)科举之习。前贤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时好。则心地恬愉。自无怵迫之累。○以科举为为亲而不为为己之学。只是无志。以科业为妨实学。不知曾妨饮食否。只是无志也。
右两节朱夫子语也。今金养而有志于学。而惧其科业为累。其志殊可尚。苟能服膺斯语。庶遂其志也欤。
功夫易间断。义理难推寻。而岁月如流。甚可忧惧。奈何奈何。
右二十三字。即朱夫子与吕东莱书一段也。今余与金养而相守经夏。昕夕讲劘。专在朱书。而尽了一帙矣。养而临归取此一段。请余写与。其意岂寻常哉。噫。朱书实义理府库也。义理推寻。莫要于是书。苟能有觑乎此则功夫虽欲间断而自不能已焉。今养而将不知其度几许岁月而常有忧惧之心则其进何可量也。余所期望于养而者于是益大。遂书此以贻之。阏逢困敦中秋上浣。性潭老夫。
为芮君国烈写与五十六字。仍书其后。
风月无边。庭草交翠。扬休山立。玉色金声。规圆矩方。绳直准平。閒中今古。醉里乾坤。精思力践。妙契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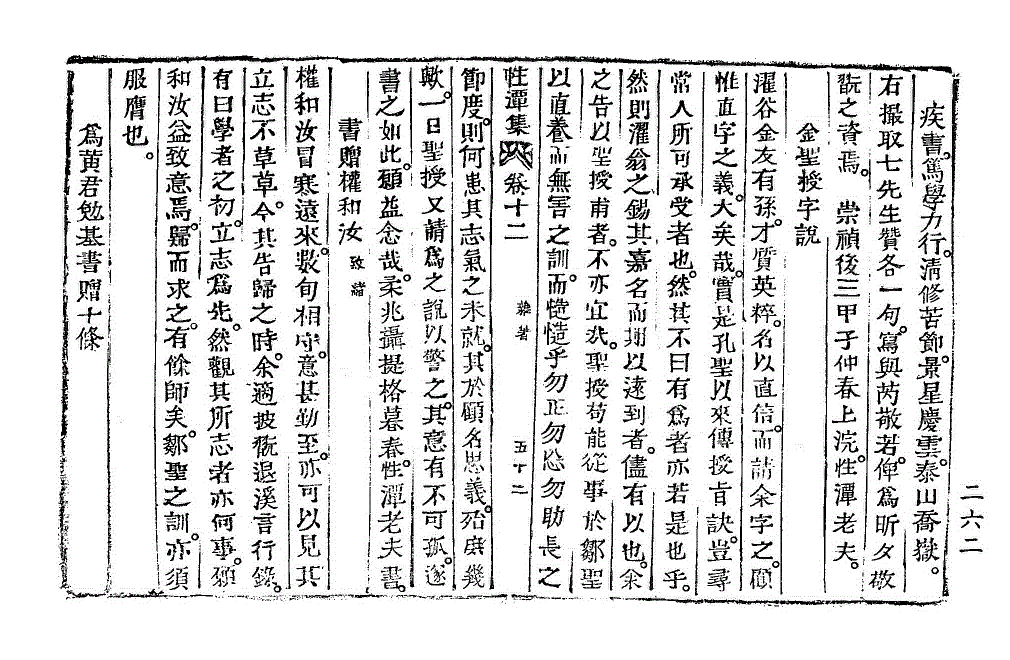 疾书。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景星庆云。泰山乔岳。
疾书。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景星庆云。泰山乔岳。右撮取七先生赞各一句。写与芮敬若。俾为昕夕敬玩之资焉。 崇祯后三甲子仲春上浣。性潭老夫。
金圣授字说
濯谷金友有孙。才质英粹。名以直信。而请余字之。顾惟直字之义。大矣哉。实是孔圣以来传授旨诀。岂寻常人所可承受者也。然其不曰有为者亦若是也乎。然则濯翁之锡其嘉名而期以远到者。尽有以也。余之告以圣授甫者。不亦宜哉。圣授苟能从事于邹圣以直养而无害之训。而慥慥乎勿正勿忘勿助长之节度。则何患其志气之未就。其于顾名思义。殆庶几欤。一日圣授又请为之说以警之。其意有不可孤。遂书之如此。愿益念哉。柔兆摄提格暮春。性潭老夫书。
书赠权和汝(致绪)
权和汝冒寒远来。数旬相守。意甚勤至。亦可以见其立志不草草。今其告归之时。余适披玩退溪言行录。有曰学者之初。立志为先。然观其所志者亦何事。愿和汝益致意焉。归而求之。有馀师矣。邹圣之训。亦须服膺也。
为黄君勉基书赠十条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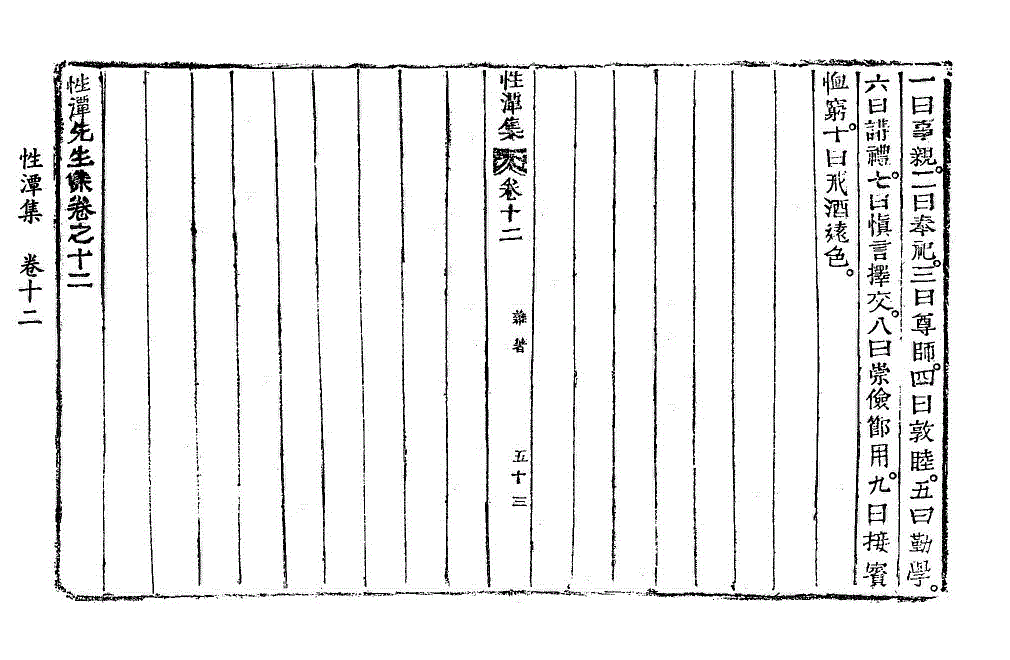 一曰事亲。二曰奉祀。三曰尊师。四曰敦睦。五曰勤学。六曰讲礼。七曰慎言择交。八曰崇俭节用。九曰接宾恤穷。十曰戒酒远色。
一曰事亲。二曰奉祀。三曰尊师。四曰敦睦。五曰勤学。六曰讲礼。七曰慎言择交。八曰崇俭节用。九曰接宾恤穷。十曰戒酒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