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x 页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书
书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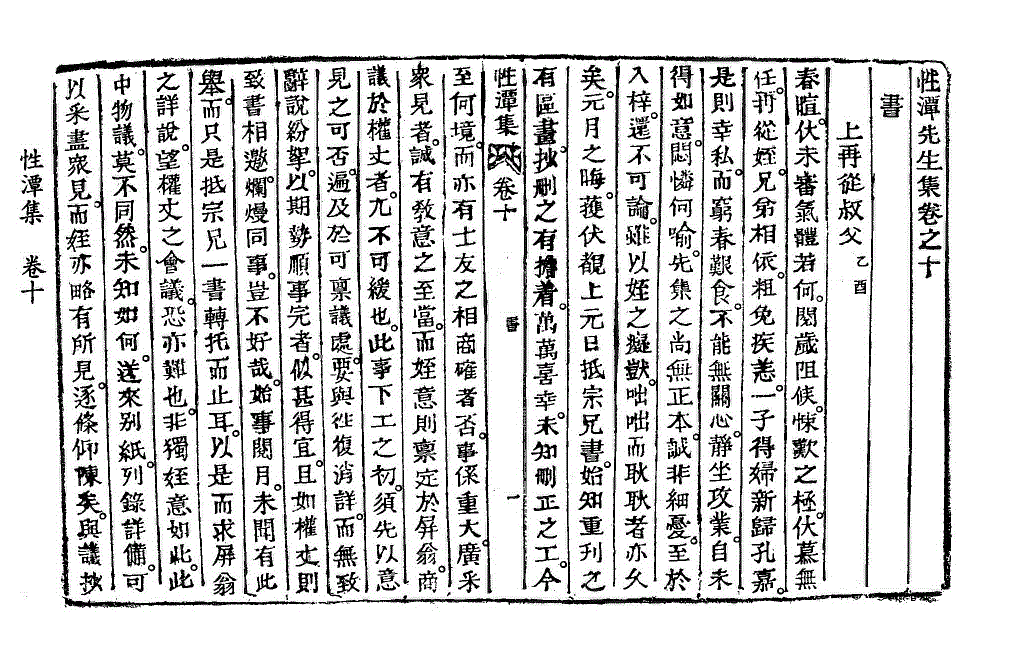 上再从叔父(乙酉)
上再从叔父(乙酉)春暄。伏未审气体若何。阅岁阻候。悚叹之极。伏慕无任。再从侄。兄弟相依。粗免疾恙。一子得妇新归孔嘉。是则幸私。而穷春艰食。不能无关心。静坐攻业。自未得如意。闷怜何喻。先集之尚无正本。诚非细忧。至于入梓。还不可论。虽以侄之痴呆。咄咄而耿耿者亦久矣。元月之晦。获伏睹上元日抵宗兄书。始知重刊之有区画。抄删之有担着。万万喜幸。未知删正之工。今至何境。而亦有士友之相商确者否。事系重大。广采众见者。诚有教意之至当。而侄意则禀定于屏翁。商议于权丈者。尤不可缓也。此事下工之初。须先以意见之可否。遍及于可禀议处。要与往复消详。而无致辞说纷挐。以期势顺事完者。似甚得宜。且如权丈则致书相邀。烂熳同事。岂不好哉。始事阅月。未闻有此举。而只是抵宗兄一书转托而止耳。以是而求屏翁之详说。望权丈之会议。恐亦难也。非独侄意如此。此中物议。莫不同然。未知如何。送来别纸。列录详备。可以采尽众见。而侄亦略有所见。逐条仰陈矣。与议抄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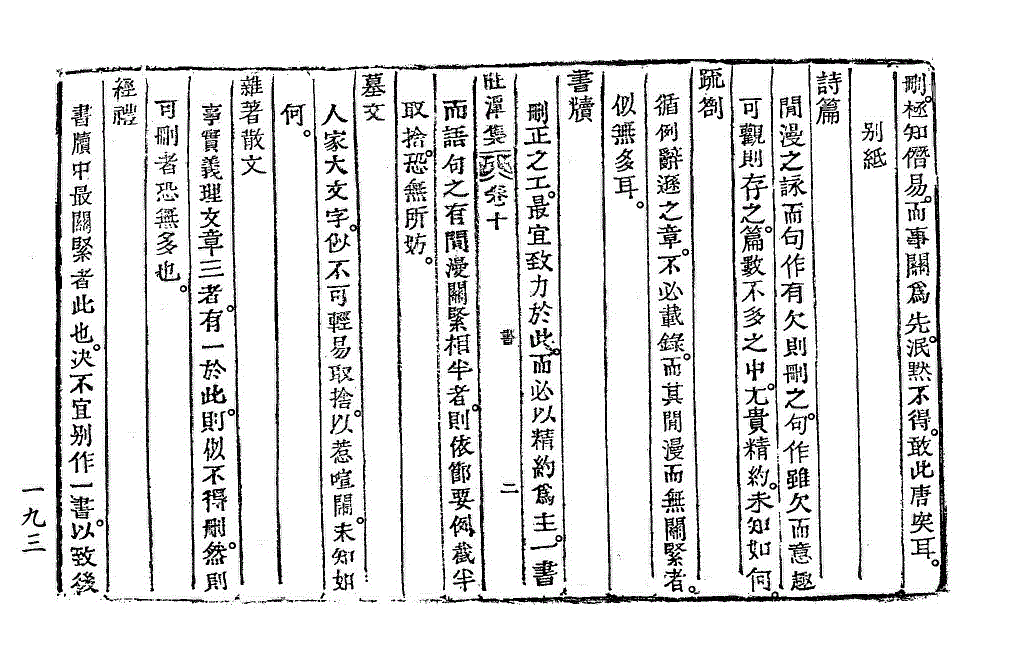 删。极知僭易。而事关为先。泯默不得。敢此唐突耳。
删。极知僭易。而事关为先。泯默不得。敢此唐突耳。别纸
诗篇
閒漫之咏而句作有欠则删之。句作虽欠而意趣可观则存之。篇数不多之中。尤贵精约。未知如何。
疏劄
循例辞逊之章。不必载录。而其閒漫而无关紧者。似无多耳。
书牍
删正之工。最宜致力于此。而必以精约为主。一书而语句之有閒漫关紧相半者。则依节要例截半取舍。恐无所妨。
墓文
人家大文字。似不可轻易取舍。以惹喧闹。未知如何。
杂著散文
事实义理文章三者。有一于此。则似不得删。然则可删者恐无多也。
经礼
书牍中最关紧者此也。决不宜别作一书。以致后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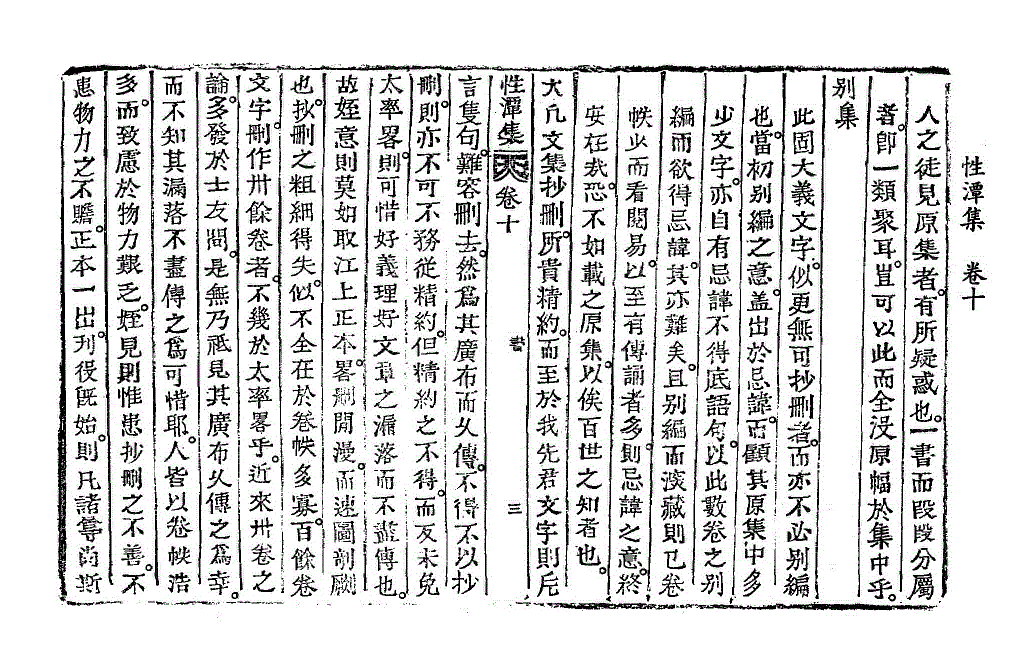 人之徒见原集者。有所疑惑也。一书而段段分属者。即一类聚耳。岂可以此而全没原幅于集中乎。
人之徒见原集者。有所疑惑也。一书而段段分属者。即一类聚耳。岂可以此而全没原幅于集中乎。别集
此固大义文字。似更无可抄删者。而亦不必别编也。当初别编之意。盖出于忌讳。而顾其原集中多少文字。亦自有忌讳不得底语句。以此数卷之别编而欲得忌讳。其亦难矣。且别编而深藏则已卷帙少而看阅易。以至有传诵者多。则忌讳之意。终安在哉。恐不如载之原集。以俟百世之知者也。
大凡文集抄删。所贵精约。而至于我先君文字则片言只句。难容删去。然为其广布而久传。不得不以抄删。则亦不可不务从精约。但精约之不得。而反未免太率略。则可惜好义理好文章之漏落而不尽传也。故侄意则莫如取江上正本。略删閒漫。而速图剞劂也。抄删之粗细得失。似不全在于卷帙多寡。百馀卷文字。删作卅馀卷者。不几于太率略乎。近来卅卷之论。多发于士友间。是无乃祗见其广布久传之为幸。而不知其漏落不尽传之为可惜耶。人皆以卷帙浩多。而致虑于物力艰乏。侄见则惟患抄删之不善。不患物力之不赡。正本一出。刊役既始。则凡诸尊尚斯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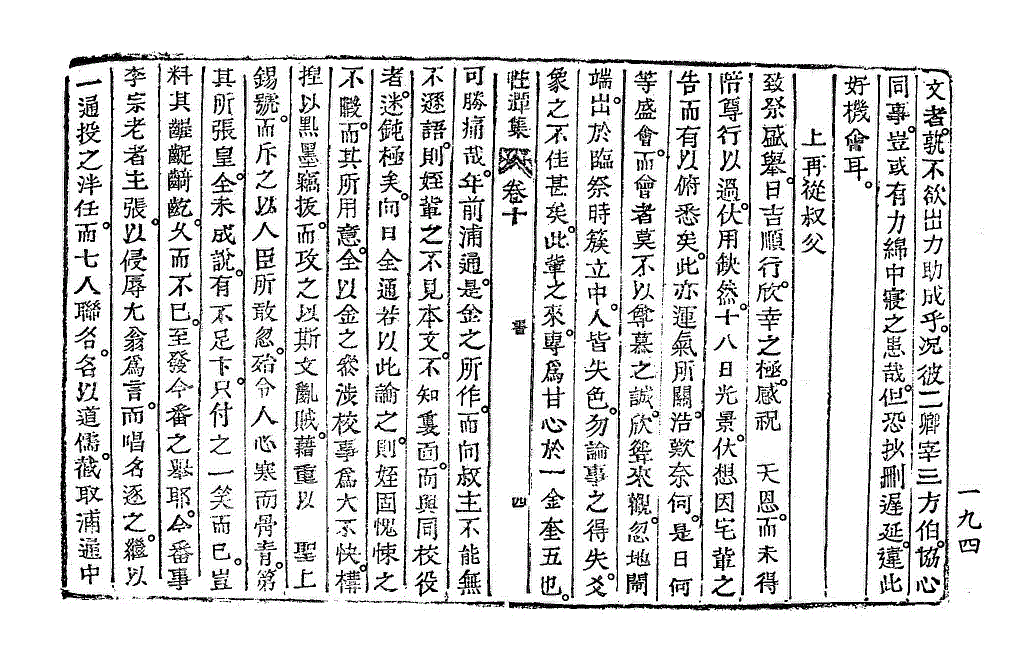 文者。孰不欲出力助成乎。况彼二卿宰三方伯。协心同事。岂或有力绵中寝之患哉。但恐抄删迟延。违此好机会耳。
文者。孰不欲出力助成乎。况彼二卿宰三方伯。协心同事。岂或有力绵中寝之患哉。但恐抄删迟延。违此好机会耳。上再从叔父
致祭盛举。日吉顺行。欣幸之极。感祝 天恩。而未得陪尊行以过。伏用缺然。十八日光景。伏想因宅辈之告而有以俯悉矣。此亦运气所关。浩叹奈何。是日何等盛会。而会者莫不以尊慕之诚。欣耸来观。忽地闹端。出于临祭时簇立中。人皆失色。勿论事之得失。爻象之不佳甚矣。此辈之来。专为甘心于一金奎五也。可胜痛哉。年前浦通。是金之所作。而向叔主不能无不逊语。则侄辈之不见本文。不知里面。而与同校役者。迷钝极矣。向日全通若以此论之。则侄固愧悚之不暇。而其所用意。全以金之参涉校事为大不快。构捏以䵝墨窃拔。而攻之以斯文乱贼。藉重以 圣上锡号。而斥之以人臣所敢忽。殆令人心寒而骨青。第其所张皇。全未成说。有不足卞。只付之一笑而已。岂料其龌龊齮龁。久而不已。至发今番之举耶。今番事李宗老者主张。以侵辱尤翁为言。而唱名逐之。继以一通投之泮任。而七人联名。名以道儒。截取浦通中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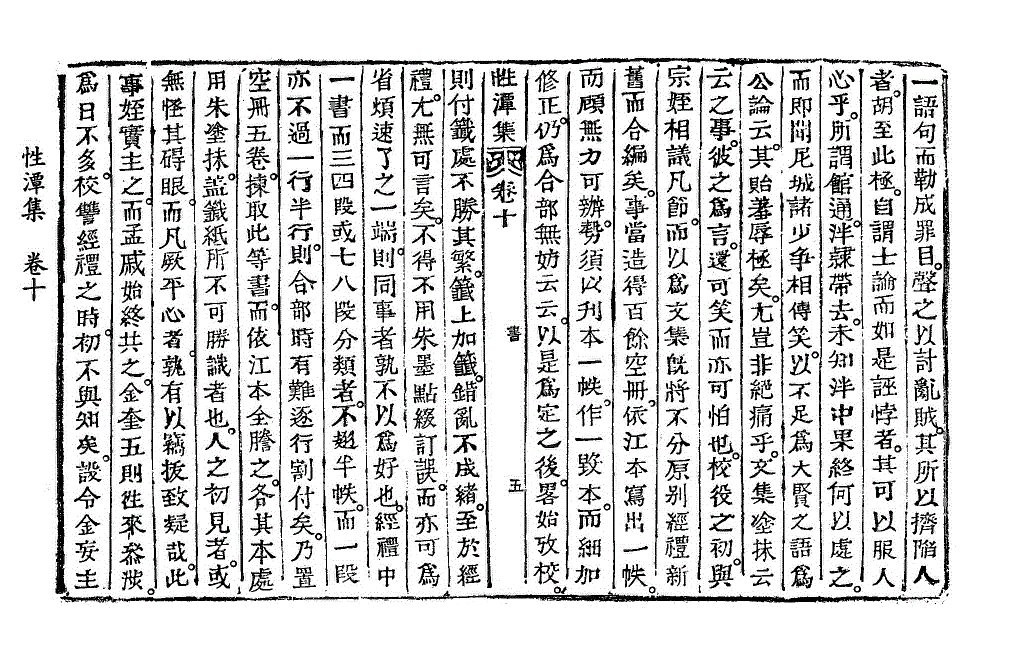 一语句而勒成罪目。声之以讨乱贼。其所以挤陷人者。胡至此极。自谓士论而如是诬悖者。其可以服人心乎。所谓馆通。泮隶带去。未知泮中果终何以处之。而即闻尼城诸少争相传笑。以不足为大贤之语为公论云。其贻羞辱极矣。尤岂非绝痛乎。文集涂抹云云之事。彼之为言。还可笑而亦可怕也。校役之初。与宗侄相议凡节。而以为文集既将不分原别经礼新旧而合编矣。事当造得百馀空册。依江本写出一帙。而顾无力可办。势须以刊本一帙。作一毁本。而细加修正。仍为合部无妨云云。以是为定之后。略始考校。则付签处不胜其繁。签上加签。错乱不成绪。至于经礼。尤无可言矣。不得不用朱墨点缀订误。而亦可为省烦速了之一端。则同事者孰不以为好也。经礼中一书而三四段或七八段分类者。不翅半帙。而一段亦不过一行半行。则合部时有难逐行割付矣。乃置空册五卷。拣取此等书。而依江本全誊之。各其本处用朱涂抹。盖签纸所不可胜识者也。人之初见者。或无怪其碍眼。而凡厥平心者。孰有以窃拔致疑哉。此事侄实主之。而孟戚始终共之。金奎五则往来参涉。为日不多。校雠经礼之时。初不与知矣。设令金妄主
一语句而勒成罪目。声之以讨乱贼。其所以挤陷人者。胡至此极。自谓士论而如是诬悖者。其可以服人心乎。所谓馆通。泮隶带去。未知泮中果终何以处之。而即闻尼城诸少争相传笑。以不足为大贤之语为公论云。其贻羞辱极矣。尤岂非绝痛乎。文集涂抹云云之事。彼之为言。还可笑而亦可怕也。校役之初。与宗侄相议凡节。而以为文集既将不分原别经礼新旧而合编矣。事当造得百馀空册。依江本写出一帙。而顾无力可办。势须以刊本一帙。作一毁本。而细加修正。仍为合部无妨云云。以是为定之后。略始考校。则付签处不胜其繁。签上加签。错乱不成绪。至于经礼。尤无可言矣。不得不用朱墨点缀订误。而亦可为省烦速了之一端。则同事者孰不以为好也。经礼中一书而三四段或七八段分类者。不翅半帙。而一段亦不过一行半行。则合部时有难逐行割付矣。乃置空册五卷。拣取此等书。而依江本全誊之。各其本处用朱涂抹。盖签纸所不可胜识者也。人之初见者。或无怪其碍眼。而凡厥平心者。孰有以窃拔致疑哉。此事侄实主之。而孟戚始终共之。金奎五则往来参涉。为日不多。校雠经礼之时。初不与知矣。设令金妄主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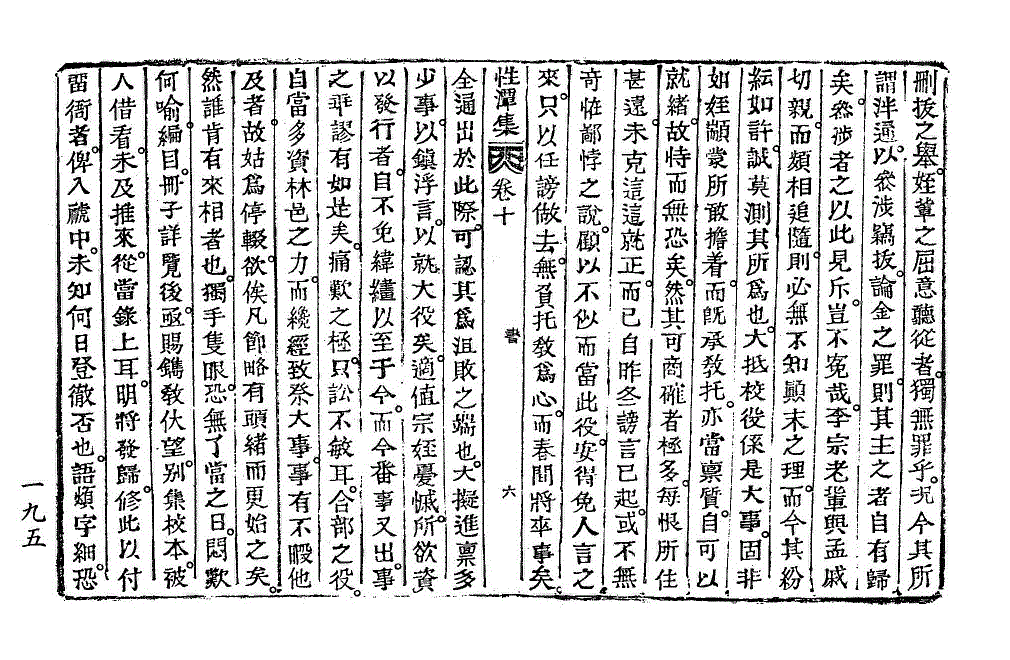 删拔之举。侄辈之屈意听从者。独无罪乎。况今其所谓泮通。以参涉窃拔。论金之罪。则其主之者自有归矣。参涉者之以此见斥。岂不冤哉。李宗老辈与孟戚切亲。而频相追随。则必无不知颠末之理。而今其纷纭如许。诚莫测其所为也。大抵校役系是大事。固非如侄颛蒙所敢担着。而既承教托。亦当禀质。自可以就绪。故恃而无恐矣。然其可商确者极多。每恨所住甚远。未克这这就正。而已自昨冬谤言已起。或不无奇怪鄙悖之说。顾以不似而当此役。安得免人言之来。只以任谤做去。无负托教为心。而春间将卒事矣。全通出于此际。可认其为沮败之端也。大拟进禀多少事。以镇浮言。以就大役矣。适值宗侄忧戚。所欲资以发行者。自不免纬繣以至于今。而今番事又出。事之乖谬有如是矣。痛叹之极。只讼不敏耳。合部之役。自当多资林邑之力。而才经致祭大事。事有不暇他及者。故姑为停辍。欲俟凡节略有头绪而更始之矣。然谁肯有来相者也。独手只眼。恐无了当之日。闷叹何喻。编目。册子详览后。亟赐镌教伏望。别集校本。被人借看。未及推来。从当录上耳。明将发归。修此以付留衙者。俾入褫中。未知何日登彻否也。语烦字细。恐
删拔之举。侄辈之屈意听从者。独无罪乎。况今其所谓泮通。以参涉窃拔。论金之罪。则其主之者自有归矣。参涉者之以此见斥。岂不冤哉。李宗老辈与孟戚切亲。而频相追随。则必无不知颠末之理。而今其纷纭如许。诚莫测其所为也。大抵校役系是大事。固非如侄颛蒙所敢担着。而既承教托。亦当禀质。自可以就绪。故恃而无恐矣。然其可商确者极多。每恨所住甚远。未克这这就正。而已自昨冬谤言已起。或不无奇怪鄙悖之说。顾以不似而当此役。安得免人言之来。只以任谤做去。无负托教为心。而春间将卒事矣。全通出于此际。可认其为沮败之端也。大拟进禀多少事。以镇浮言。以就大役矣。适值宗侄忧戚。所欲资以发行者。自不免纬繣以至于今。而今番事又出。事之乖谬有如是矣。痛叹之极。只讼不敏耳。合部之役。自当多资林邑之力。而才经致祭大事。事有不暇他及者。故姑为停辍。欲俟凡节略有头绪而更始之矣。然谁肯有来相者也。独手只眼。恐无了当之日。闷叹何喻。编目。册子详览后。亟赐镌教伏望。别集校本。被人借看。未及推来。从当录上耳。明将发归。修此以付留衙者。俾入褫中。未知何日登彻否也。语烦字细。恐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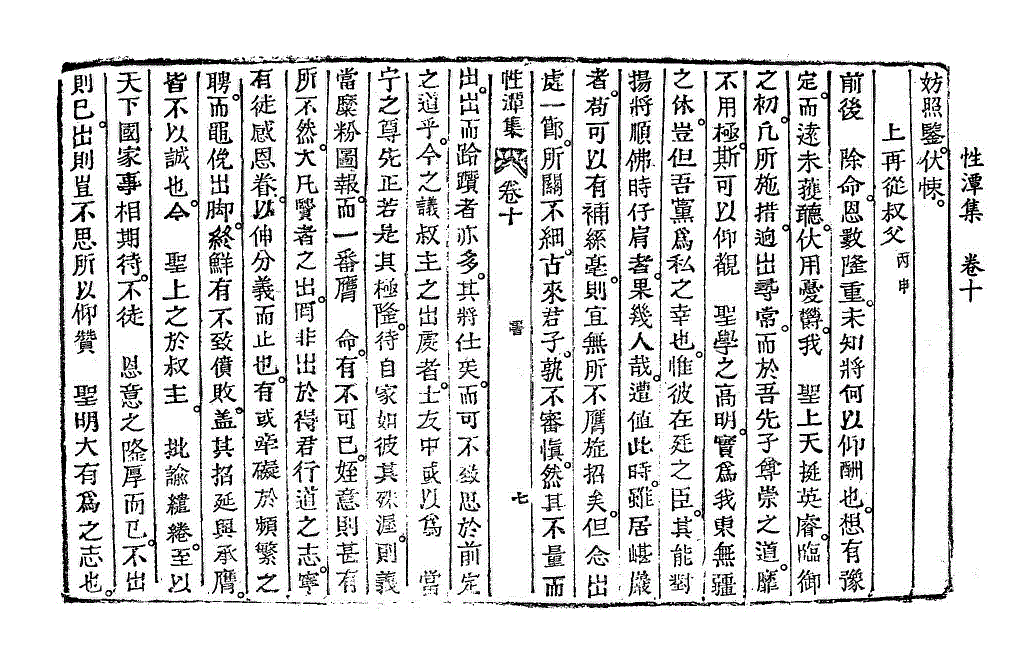 妨照鉴。伏悚。
妨照鉴。伏悚。上再从叔父(丙申)
前后 除命。恩数隆重。未知将何以仰酬也。想有豫定。而远未获听。伏用忧郁。我 圣上天挺英睿。临御之初。凡所施措。迥出寻常。而于吾先子尊崇之道。靡不用极。斯可以仰睹 圣学之高明。实为我东无疆之休。岂但吾党为私之幸也。惟彼在廷之臣。其能对扬将顺佛时仔肩者。果几人哉。遭值此时。虽居嵁岩者。苟可以有补丝毫。则宜无所不膺㫌招矣。但念出处一节。所关不细。古来君子。孰不审慎。然其不量而出。出而跲踬者亦多。其将仕矣。而可不致思于前定之道乎。今之议叔主之出处者。士友中或以为 当宁之尊先正若是其极隆。待自家如彼其殊渥。则义当糜粉图报。而一番膺 命。有不可已。侄意则甚有所不然。大凡贤者之出。罔非出于得君行道之志。宁有徒感恩眷。以伸分义而止也。有或牵碍于频繁之聘。而黾俛出脚。终鲜有不致偾败。盖其招延与承膺。皆不以诚也。今 圣上之于叔主。 批谕缱绻。至以天下国家事相期待。不徒 恩意之隆厚而已。不出则已。出则岂不思所以仰赞 圣明大有为之志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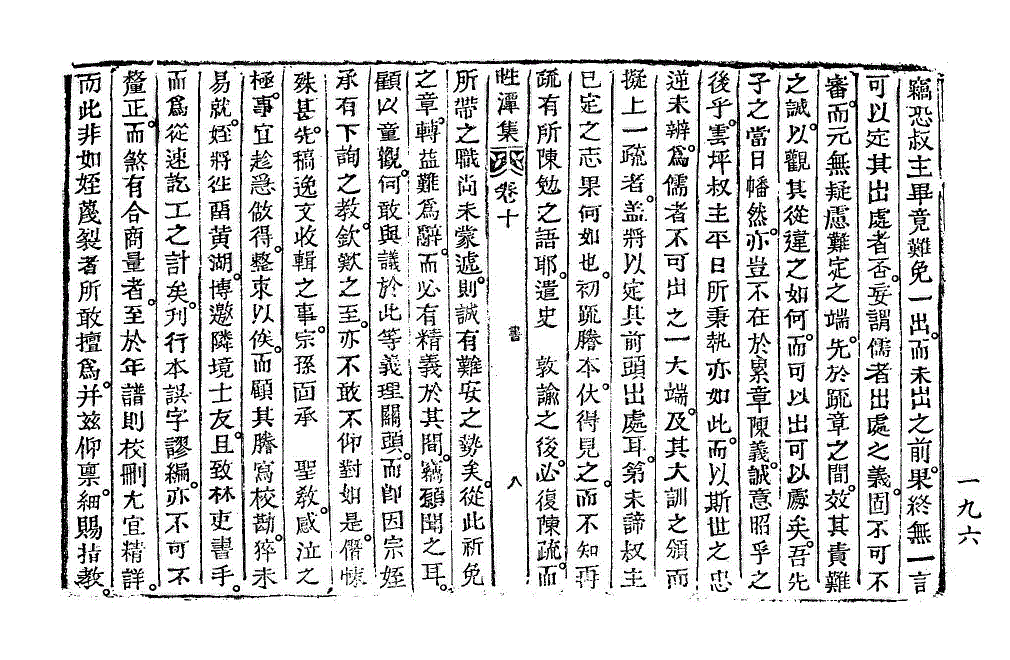 窃恐叔主毕竟难免一出。而未出之前。果终无一言可以定其出处者否。妄谓儒者出处之义。固不可不审。而元无疑虑难定之端。先于疏章之间。效其责难之诚。以观其从违之如何。而可以出可以处矣。吾先子之当日幡然。亦岂不在于累章陈义。诚意昭孚之后乎。云坪叔主平日所秉执亦如此。而以斯世之忠逆未辨。为儒者不可出之一大端。及其大训之颁而拟上一疏者。盖将以定其前头出处耳。第未谛叔主已定之志果何如也。初疏誊本。伏得见之。而不知再疏有所陈勉之语耶。遣史 敦谕之后。必复陈疏。而所带之职尚未蒙递。则诚有难安之势矣。从此祈免之章。转益难为辞。而必有精义于其间。窃愿闻之耳。顾以童观。何敢与议于此等义理关头。而即因宗侄承有下询之教。钦叹之至。亦不敢不仰对如是。僭悚殊甚。先稿逸文收辑之事。宗孙面承 圣教。感泣之极。事宜趁急做得。整束以俟。而顾其誊写校勘。猝未易就。侄将往留黄湖。博邀邻境士友。且致林吏书手。而为从速讫工之计矣。刊行本误字谬编。亦不可不釐正。而煞有合商量者。至于年谱则校删尤宜精详。而此非如侄蔑裂者所敢擅为。并玆仰禀。细赐指教。
窃恐叔主毕竟难免一出。而未出之前。果终无一言可以定其出处者否。妄谓儒者出处之义。固不可不审。而元无疑虑难定之端。先于疏章之间。效其责难之诚。以观其从违之如何。而可以出可以处矣。吾先子之当日幡然。亦岂不在于累章陈义。诚意昭孚之后乎。云坪叔主平日所秉执亦如此。而以斯世之忠逆未辨。为儒者不可出之一大端。及其大训之颁而拟上一疏者。盖将以定其前头出处耳。第未谛叔主已定之志果何如也。初疏誊本。伏得见之。而不知再疏有所陈勉之语耶。遣史 敦谕之后。必复陈疏。而所带之职尚未蒙递。则诚有难安之势矣。从此祈免之章。转益难为辞。而必有精义于其间。窃愿闻之耳。顾以童观。何敢与议于此等义理关头。而即因宗侄承有下询之教。钦叹之至。亦不敢不仰对如是。僭悚殊甚。先稿逸文收辑之事。宗孙面承 圣教。感泣之极。事宜趁急做得。整束以俟。而顾其誊写校勘。猝未易就。侄将往留黄湖。博邀邻境士友。且致林吏书手。而为从速讫工之计矣。刊行本误字谬编。亦不可不釐正。而煞有合商量者。至于年谱则校删尤宜精详。而此非如侄蔑裂者所敢擅为。并玆仰禀。细赐指教。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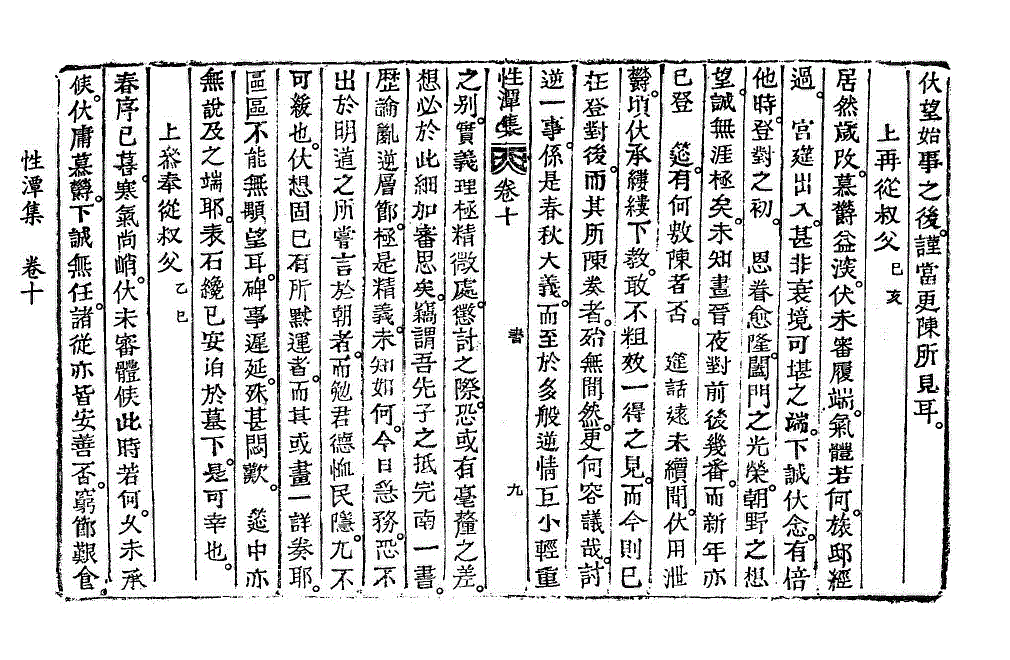 伏望始事之后。谨当更陈所见耳。
伏望始事之后。谨当更陈所见耳。上再从叔父(己亥)
居然岁改。慕郁益深。伏未审履端。气体若何。旅邸经过。 宫筵出入。甚非衰境可堪之端。下诚伏念。有倍他时。登对之初。 恩眷愈隆。阖门之光荣。朝野之想望。诚无涯极矣。未知昼晋夜对前后几番。而新年亦已登 筵。有何敷陈者否。 筵话远未续闻。伏用泄郁。顷伏承缕缕下教。敢不粗效一得之见。而今则已在登对后。而其所陈奏者。殆无间然。更何容议哉。讨逆一事。系是春秋大义。而至于多般逆情巨小轻重之别。实义理极精微处。惩讨之际。恐或有毫釐之差。想必于此细加审思矣。窃谓吾先子之抵完南一书。历论乱逆层节。极是精义。未知如何。今日急务。恐不出于明道之所尝言于朝者。而勉君德恤民隐。尤不可缓也。伏想固已有所默运者。而其或画一详奏耶。区区不能无颙望耳。碑事迟延。殊甚闷叹。 筵中亦无说及之端耶。表石才已安泊于墓下。是可幸也。
上参奉从叔父(乙巳)
春序已暮。寒气尚峭。伏未审体候此时若何。久未承候。伏庸慕郁。下诚无任。诸从亦皆安善否。穷节艰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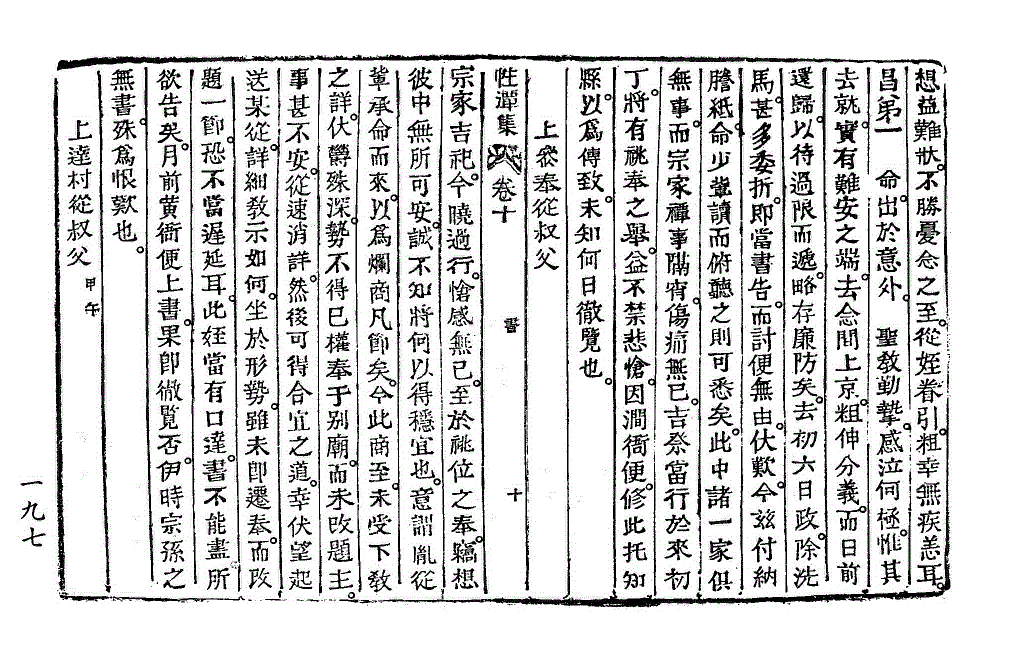 想益难状。不胜忧念之至。从侄眷引。粗幸无疾恙耳。昌弟一 命。出于意外。 圣教勤挚。感泣何极。惟其去就。实有难安之端。去念间上京。粗伸分义。而日前还归。以待过限而递。略存廉防矣。去初六日政。除洗马。甚多委折。即当书告。而讨便无由。伏叹。今玆付纳誊纸。命少辈读而俯听之则可悉矣。此中诸一家俱无事。而宗家禫事隔宵。伤痛无已。吉祭当行于来初丁。将有祧奉之举。益不禁悲怆。因涧衙便。修此托知县。以为传致。未知何日彻览也。
想益难状。不胜忧念之至。从侄眷引。粗幸无疾恙耳。昌弟一 命。出于意外。 圣教勤挚。感泣何极。惟其去就。实有难安之端。去念间上京。粗伸分义。而日前还归。以待过限而递。略存廉防矣。去初六日政。除洗马。甚多委折。即当书告。而讨便无由。伏叹。今玆付纳誊纸。命少辈读而俯听之则可悉矣。此中诸一家俱无事。而宗家禫事隔宵。伤痛无已。吉祭当行于来初丁。将有祧奉之举。益不禁悲怆。因涧衙便。修此托知县。以为传致。未知何日彻览也。上参奉从叔父
宗家吉祀。今晓过行。怆感无已。至于祧位之奉。窃想彼中无所可安。诚不知将何以得稳宜也。意谓胤从辈承命而来。以为烂商凡节矣。今此商至。未受下教之详。伏郁殊深。势不得已权奉于别庙。而未改题主。事甚不安。从速消详。然后可得合宜之道。幸伏望起送某从。详细教示如何。坐于形势。虽未即迁奉。而改题一节。恐不当迟延耳。此侄当有口达。书不能尽所欲告矣。月前黄衙便上书。果即彻览否。伊时宗孙之无书。殊为恨叹也。
上达村从叔父(甲午)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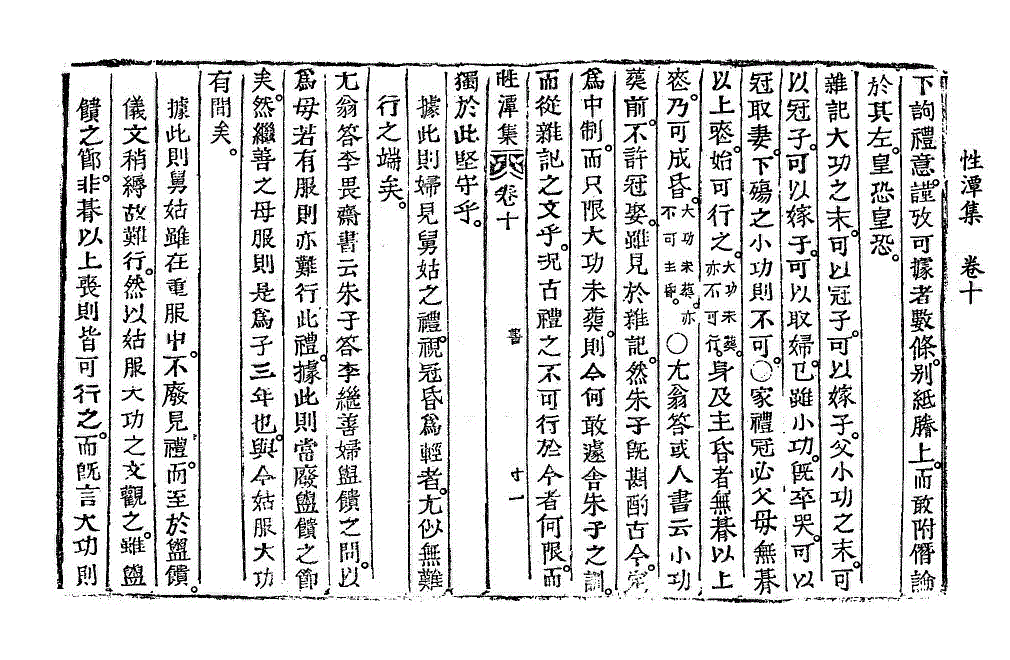 下询礼意。谨考可据者数条。别纸誊上。而敢附僭论于其左。皇恐皇恐。
下询礼意。谨考可据者数条。别纸誊上。而敢附僭论于其左。皇恐皇恐。杂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妇。已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家礼冠必父母无期以上丧。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乃可成昏。(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尤翁答或人书云小功葬前。不许冠娶。虽见于杂记。然朱子既斟酌古今。定为中制。而只限大功未葬。则今何敢遽舍朱子之训。而从杂记之文乎。况古礼之不可行于今者何限。而独于此坚守乎。
据此则妇见舅姑之礼。视冠昏为轻者。尤似无难行之端矣。
尤翁答李畏斋书云朱子答李继善妇盥馈之问。以为母若有服则亦难行此礼。据此则当废盥馈之节矣。然继善之母服则是为子三年也。与今姑服大功有间矣。
据此则舅姑虽在重服中。不废见礼。而至于盥馈。仪文稍缛故难行。然以姑服大功之文观之。虽盥馈之节。非期以上丧则皆可行之。而既言大功则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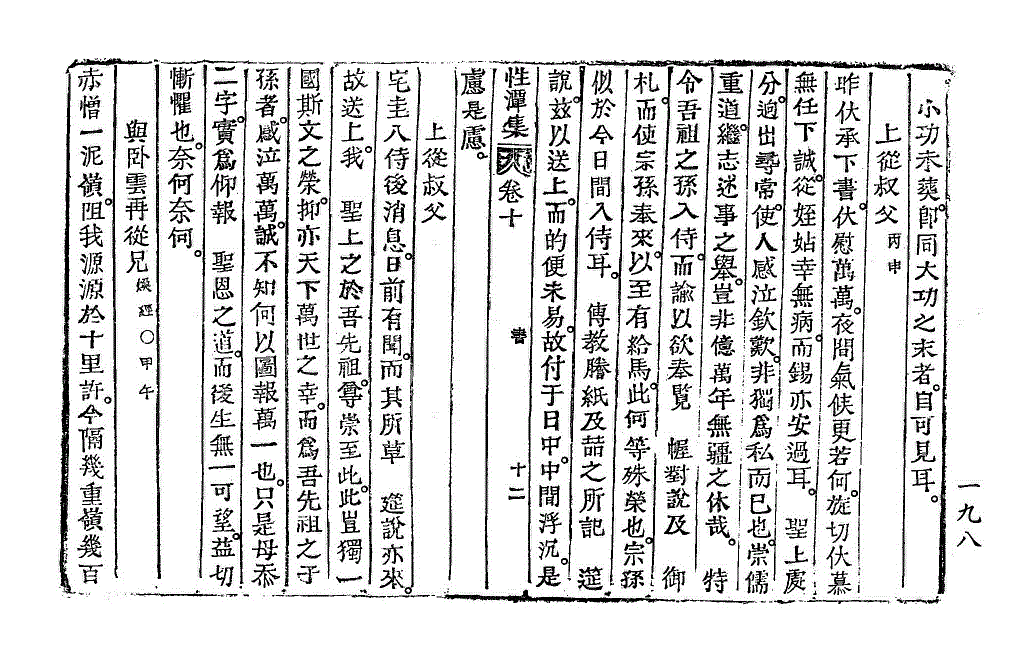 小功未葬。即同大功之末者。自可见耳。
小功未葬。即同大功之末者。自可见耳。上从叔父(丙申)
昨伏承下书。伏慰万万。夜间气候更若何。旋切伏慕无任下诚。从侄姑幸无病。而锡亦安过耳。 圣上处分。迥出寻常。使人感泣钦叹。非独为私而已也。崇儒重道。继志述事之举。岂非亿万年无疆之休哉。 特令吾祖之孙入侍。而谕以欲奉览 幄对说及 御札。而使宗孙奉来。以至有给马。此何等殊荣也。宗孙似于今日间入侍耳。 传教誊纸及哲之所记 筵说。玆以送上。而的便未易。故付于日中。中间浮沉。是虑是虑。
上从叔父
宅圭入侍后消息。日前有闻。而其所草 筵说亦来。故送上。我 圣上之于吾先祖。尊崇至此。此岂独一国斯文之荣。抑亦天下万世之幸。而为吾先祖之子孙者。感泣万万。诚不知何以图报万一也。只是毋忝二字。实为仰报 圣恩之道。而后生无一可望。益切惭惧也。奈何奈何。
与卧云再从兄(焕经○甲午)
赤憎一泥岭。阻我源源于十里许。今隔几重岭几百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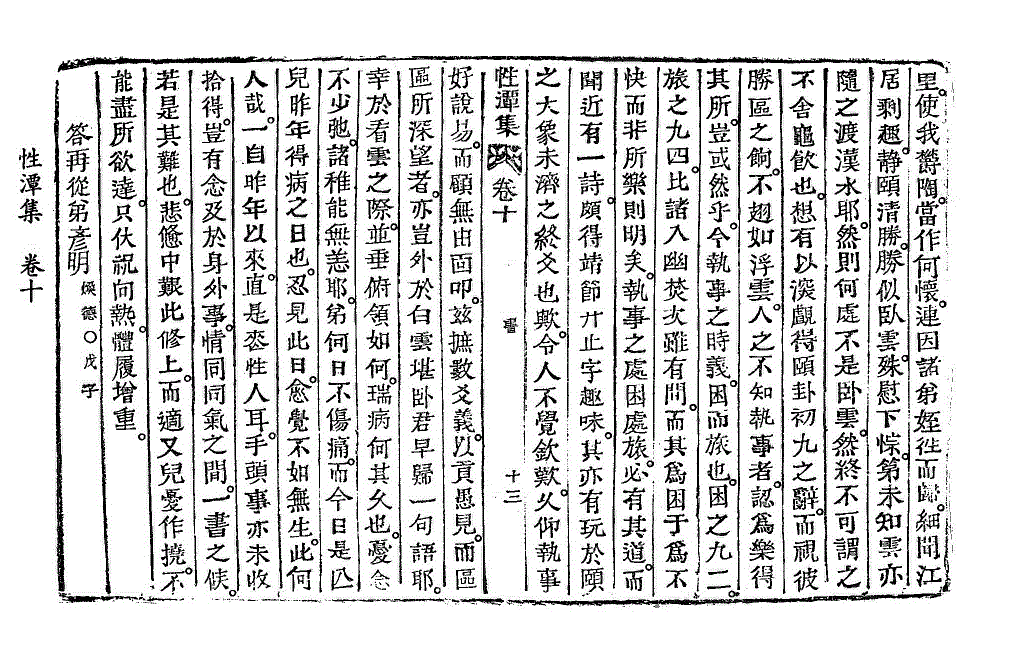 里。使我郁陶。当作何怀。连因诸弟侄往而归。细闻江居剩趣。静颐清胜。胜似卧云。殊慰下悰。第未知云亦随之渡汉水耶。然则何处不是卧云。然终不可谓之不舍龟饮也。想有以深觑得颐卦初九之辞。而视彼胜区之饷。不翅如浮云。人之不知执事者。认为乐得其所。岂或然乎。今执事之时义。困而旅也。困之九二。旅之九四。比诸入幽焚次虽有间。而其为困于为不快而非所乐则明矣。执事之处困处旅。必有其道。而闻近有一诗。颇得靖节廿止字趣味。其亦有玩于颐之大象未济之终爻也欤。令人不觉钦叹。久仰执事好说易。而顾无由面叩。玆摭数爻义。以贡愚见。而区区所深望者。亦岂外于白云堪卧君早归一句语耶。幸于看云之际。并垂俯领如何。瑞病何其久也。忧念不少弛。诸稚能无恙耶。弟何日不伤痛。而今日是亡儿昨年得病之日也。忍见此日。愈觉不如无生。此何人哉。一自昨年以来。直是丧性人耳。手头事亦未收拾得。岂有念及于身外事。情同同气之间。一书之候。若是其难也。悲惫中艰此修上。而适又儿忧作挠。不能尽所欲达。只伏祝向热。体履增重。
里。使我郁陶。当作何怀。连因诸弟侄往而归。细闻江居剩趣。静颐清胜。胜似卧云。殊慰下悰。第未知云亦随之渡汉水耶。然则何处不是卧云。然终不可谓之不舍龟饮也。想有以深觑得颐卦初九之辞。而视彼胜区之饷。不翅如浮云。人之不知执事者。认为乐得其所。岂或然乎。今执事之时义。困而旅也。困之九二。旅之九四。比诸入幽焚次虽有间。而其为困于为不快而非所乐则明矣。执事之处困处旅。必有其道。而闻近有一诗。颇得靖节廿止字趣味。其亦有玩于颐之大象未济之终爻也欤。令人不觉钦叹。久仰执事好说易。而顾无由面叩。玆摭数爻义。以贡愚见。而区区所深望者。亦岂外于白云堪卧君早归一句语耶。幸于看云之际。并垂俯领如何。瑞病何其久也。忧念不少弛。诸稚能无恙耶。弟何日不伤痛。而今日是亡儿昨年得病之日也。忍见此日。愈觉不如无生。此何人哉。一自昨年以来。直是丧性人耳。手头事亦未收拾得。岂有念及于身外事。情同同气之间。一书之候。若是其难也。悲惫中艰此修上。而适又儿忧作挠。不能尽所欲达。只伏祝向热。体履增重。答再从弟彦明(焕德○戊子)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1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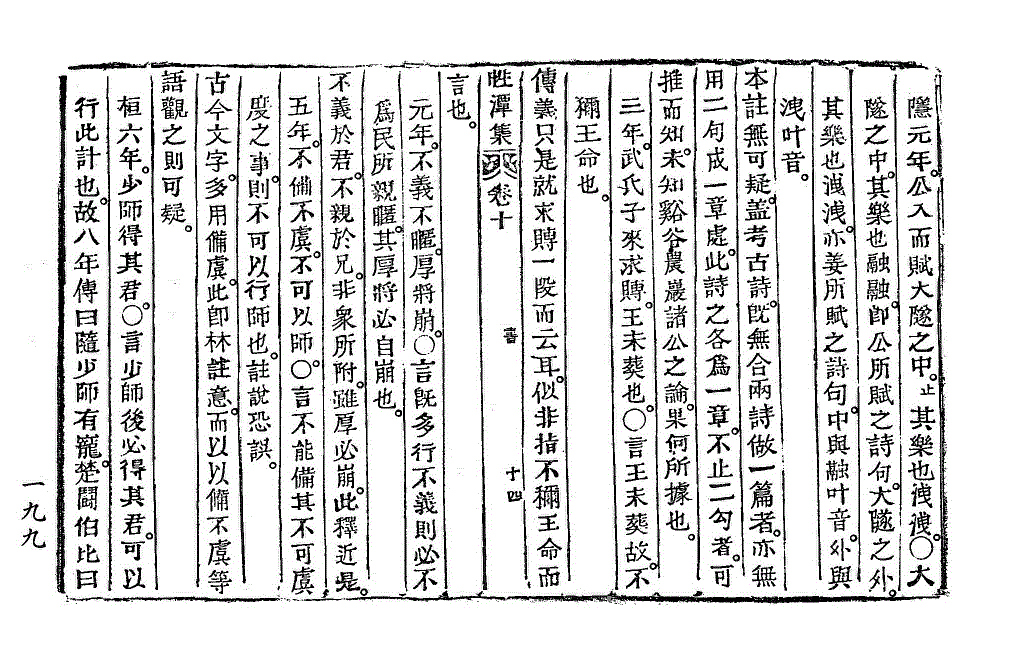 隐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止)其乐也泄泄。○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即公所赋之诗句。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亦姜所赋之诗句。中与融叶音。外与泄叶音。
隐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止)其乐也泄泄。○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即公所赋之诗句。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亦姜所赋之诗句。中与融叶音。外与泄叶音。本注无可疑。盖考古诗。既无合两诗做一篇者。亦无用二句成一章处。此诗之各为一章。不止二勾者。可推而知。未知溪谷,农岩诸公之论。果何所据也。
三年。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言王未葬故。不称王命也。
传义只是就求赙一段而云耳。似非指不称王命而言也。
元年。不义不昵。厚将崩。○言既多行不义则必不为民所亲昵。其厚将必自崩也。
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此释近是。
五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言不能备其不可虞度之事。则不可以行师也。注说恐误。
古今文字。多用备虞。此即林注意。而以以备不虞等语观之则可疑。
桓六年。少师得其君。○言少师后必得其君。可以行此计也。故八年传曰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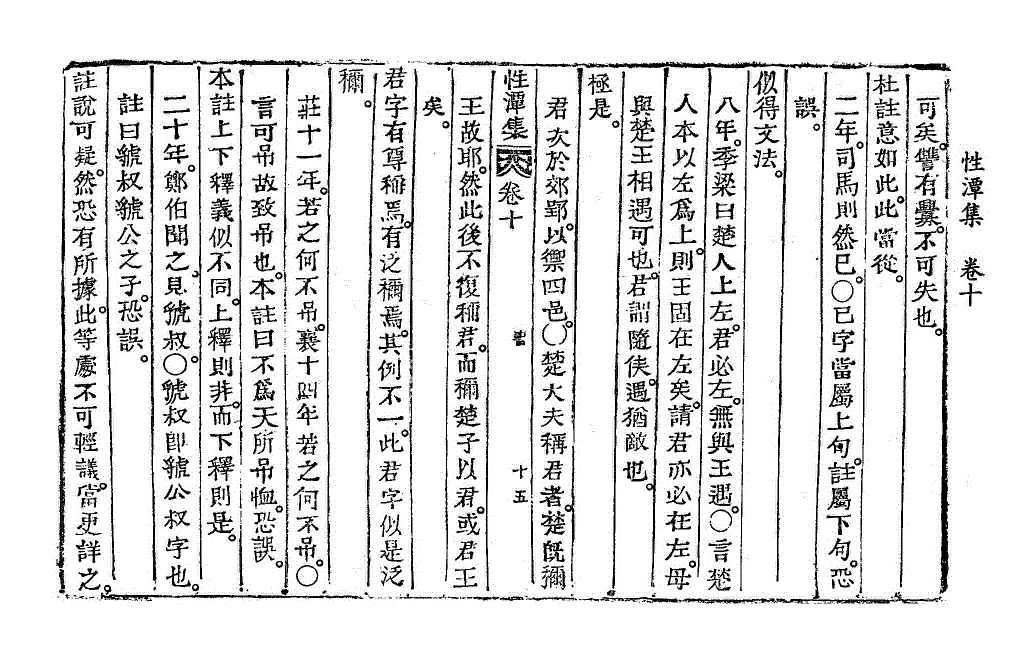 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
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杜注意如此。此当从。
二年。司马则然已。○已字当属上句。注属下句。恐误。
似得文法。
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言楚人本以左为上。则王固在左矣。请君亦必在左。毋与楚王相遇可也。君谓随侯。遇犹敌也。
极是。
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楚大夫称君者。楚既称王故耶。然此后不复称君。而称楚子以君。或君王矣。
君字有尊称焉。有泛称焉。其例不一。此君字似是泛称。
庄十一年。若之何不吊。襄十四年若之何不吊。○言可吊故致吊也。本注曰不为天所吊恤。恐误。
本注上下释义似不同。上释则非。而下释则是。
二十年。郑伯闻之。见虢叔。○虢叔即虢公叔字也。注曰虢叔虢公之子。恐误。
注说可疑。然恐有所据。此等处不可轻议。当更详之。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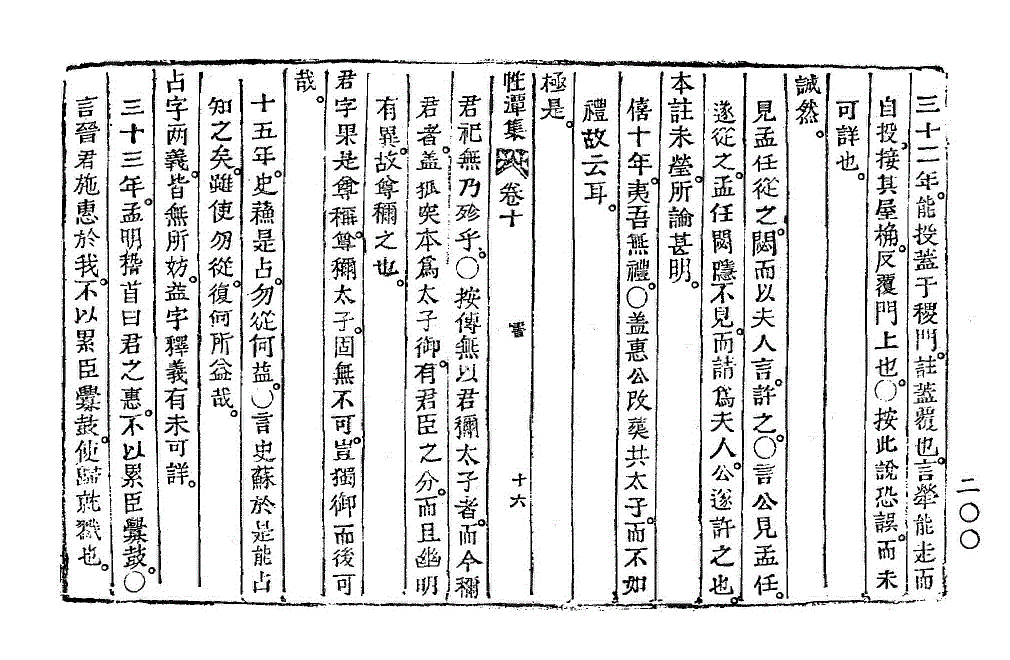 三十二年。能投盖于稷门。注盖覆也。言荦能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门上也。○按此说恐误。而未可详也。
三十二年。能投盖于稷门。注盖覆也。言荦能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门上也。○按此说恐误。而未可详也。诚然。
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言公见孟任。遂从之。孟任閟隐不见。而请为夫人。公遂许之也。
本注未莹。所论甚明。
僖十年。夷吾无礼。○盖惠公改葬共太子。而不如礼故云耳。
极是。
君祀无乃殄乎。○按传无以君称太子者。而今称君者。盖狐突本为太子御。有君臣之分。而且幽明有异。故尊称之也。
君字果是尊称。尊称太子。固无不可。岂独御而后可哉。
十五年。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言史苏于是能占知之矣。虽使勿从。复何所益哉。
占字两义。皆无所妨。益字释义有未可详。
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言晋君施惠于我。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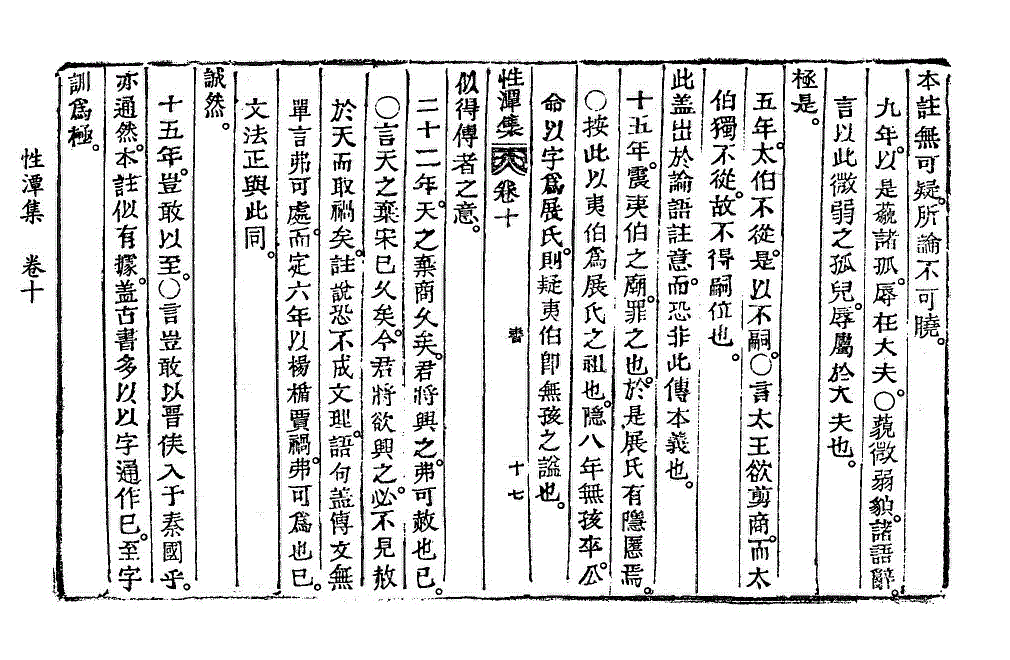 本注无可疑。所论不可晓。
本注无可疑。所论不可晓。九年。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藐微弱貌。诸语辞。言以此微弱之孤儿。辱属于大夫也。
极是。
五年。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言太王欲剪商。而太伯独不从。故不得嗣位也。
此盖出于论语注意。而恐非此传本义也。
十五年。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按此以夷伯为展氏之祖也。隐八年无孩卒。公命以字为展氏。则疑夷伯即无孩之谥也。
似得传者之意。
二十二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言天之弃宋已久矣。今君将欲兴之。必不见赦于天而取祸矣。注说恐不成文理。语句盖传文无单言弗可处。而定六年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文法正与此同。
诚然。
十五年。岂敢以至。○言岂敢以晋侯入于秦国乎。
亦通然。本注似有据。盖古书多以以字通作已。至字训为极。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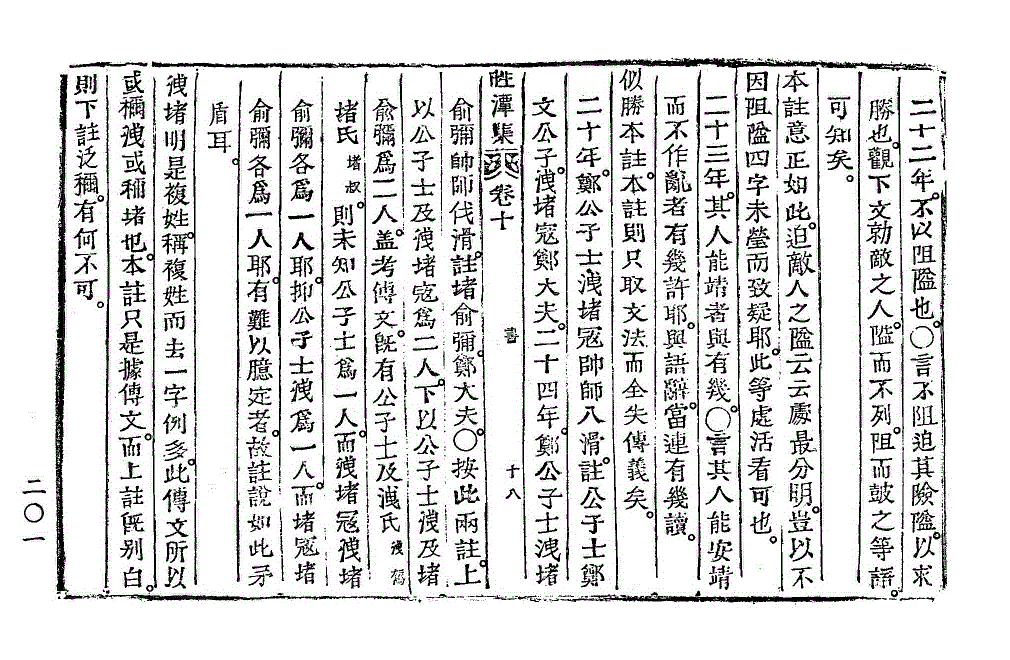 二十二年。不以阻隘也。○言不阻迫其险隘。以求胜也。观下文勍敌之人。隘而不列。阻而鼓之等语。可知矣。
二十二年。不以阻隘也。○言不阻迫其险隘。以求胜也。观下文勍敌之人。隘而不列。阻而鼓之等语。可知矣。本注意正如此。迫敌人之隘云云处最分明。岂以不因阻隘四字未莹而致疑耶。此等处活看可也。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与有几。○言其人能安靖而不作乱者有几许耶。与语辞。当连有几读。
似胜本注。本注则只取文法而全失传义矣。
二十年。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泄堵寇郑大夫。二十四年。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注堵俞弥。郑大夫。○按此两注。上以公子士及泄堵寇为二人。下以公子士泄及堵俞弥为二人。盖考传文。既有公子士及泄氏(泄驾),堵氏(堵叔)。则未知公子士为一人。而泄堵寇泄堵俞弥各为一人耶。抑公子士泄为一人。而堵寇堵俞弥各为一人耶。有难以臆定者。故注说如此矛盾耳。
泄堵明是复姓。称复姓而去一字例多。此传文所以或称泄或称堵也。本注只是据传文。而上注既别白。则下注泛称。有何不可。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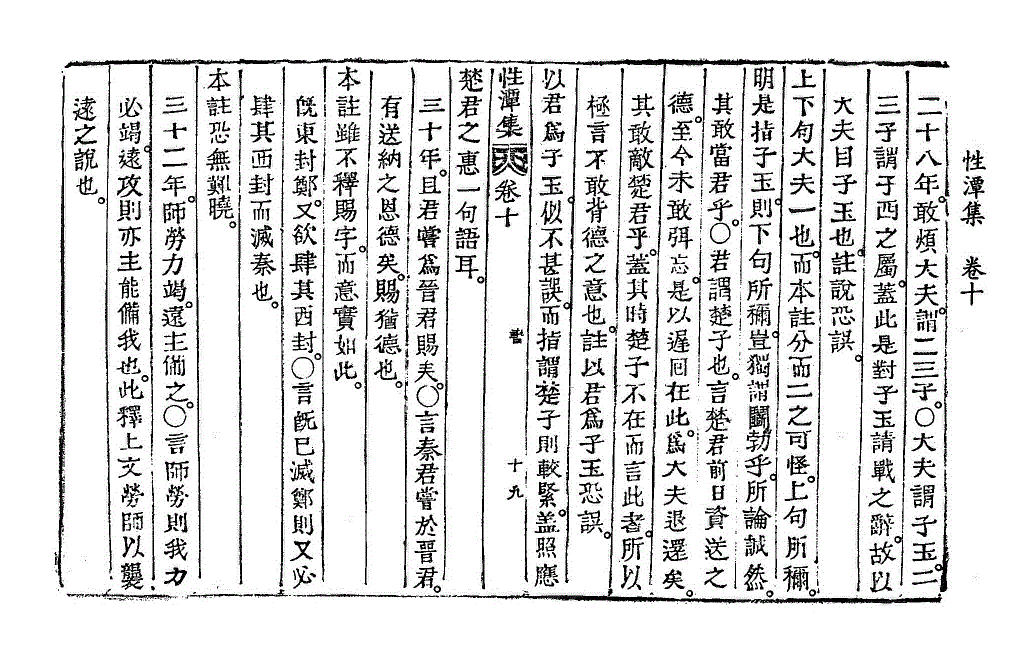 二十八年。敢烦大夫。谓二三子。○大夫谓子玉。二三子谓子西之属。盖此是对子玉请战之辞。故以大夫目子玉也。注说恐误。
二十八年。敢烦大夫。谓二三子。○大夫谓子玉。二三子谓子西之属。盖此是对子玉请战之辞。故以大夫目子玉也。注说恐误。上下句大夫一也。而本注分而二之可怪。上句所称。明是指子玉。则下句所称。岂独谓斗勃乎。所论诚然。
其敢当君乎。○君谓楚子也。言楚君前日资送之德。至今未敢弭忘。是以迟回在此。为大夫退还矣。其敢敌楚君乎。盖其时楚子不在而言此者。所以极言不敢背德之意也。注以君为子玉恐误。
以君为子玉。似不甚误。而指谓楚子则较紧。盖照应楚君之惠一句语耳。
三十年。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言秦君尝于晋君。有送纳之恩德矣。赐犹德也。
本注虽不释赐字。而意实如此。
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言既已灭郑则又必肆其西封而灭秦也。
本注恐无难晓。
三十二年。师劳力竭。远主备之。○言师劳则我力必竭。远攻则亦主能备我也。此释上文劳师以袭远之说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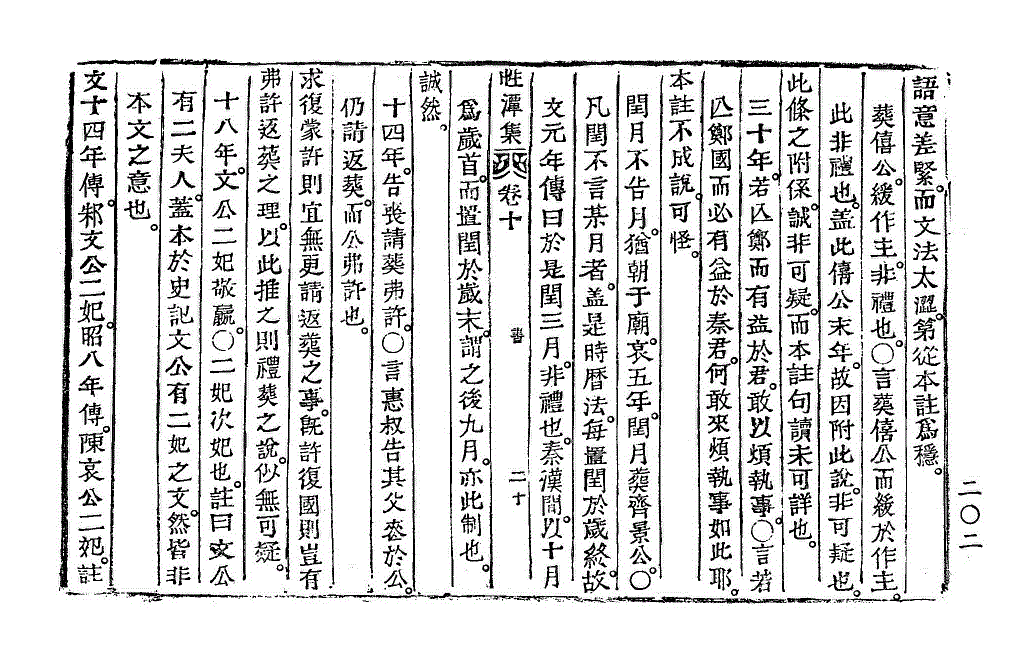 语意差紧。而文法太涩。第从本注为稳。
语意差紧。而文法太涩。第从本注为稳。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言葬僖公而缓于作主。此非礼也。盖此僖公末年。故因附此说。非可疑也。
此条之附系。诚非可疑。而本注句读未可详也。
三十年。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言若亡郑国而必有益于秦君。何敢来烦执事如此耶。
本注不成说。可怪。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凡闰不言某月者。盖是时历法。每置闰于岁终。故文元年传曰于是闰三月。非礼也。秦汉间。以十月为岁首。而置闰于岁末。谓之后九月。亦此制也。
诚然。
十四年。告丧请葬弗许。○言惠叔告其父丧于公。仍请返葬。而公弗许也。
求复蒙许则宜无更请返葬之事。既许复国则岂有弗许返葬之理。以此推之则礼葬之说。似无可疑。
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二妃次妃也。注曰文公有二夫人。盖本于史记文公有二妃之文。然皆非本文之意也。
文十四年传。邾文公二妃。昭八年传。陈哀公二妃。注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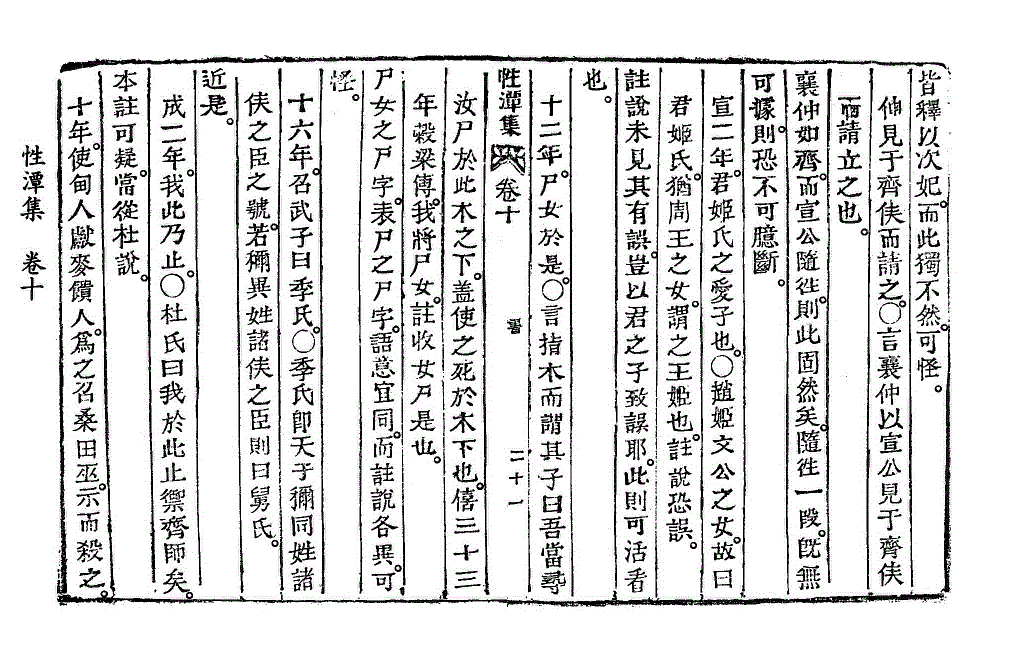 皆释以次妃。而此独不然。可怪。
皆释以次妃。而此独不然。可怪。仲见于齐侯而请之。○言襄仲以宣公见于齐侯而请立之也。
襄仲如齐。而宣公随往。则此固然矣。随往一段。既无可据。则恐不可臆断。
宣二年。君姬氏之爱子也。○赵姬文公之女。故曰君姬氏。犹周王之女。谓之王姬也。注说恐误。
注说未见其有误。岂以君之子致误耶。此则可活看也。
十二年。尸女于是。○言指木而谓其子曰吾当寻汝尸于此木之下。盖使之死于木下也。僖三十三年谷梁传。我将尸女。注收女尸是也。
尸女之尸字。表尸之尸字。语意宜同。而注说各异。可怪。
十六年。召武子曰季氏。○季氏即天子称同姓诸侯之臣之号。若称异姓诸侯之臣则曰舅氏。
近是。
成二年。我此乃止。○杜氏曰我于此止御齐师矣。
本注可疑。当从杜说。
十年。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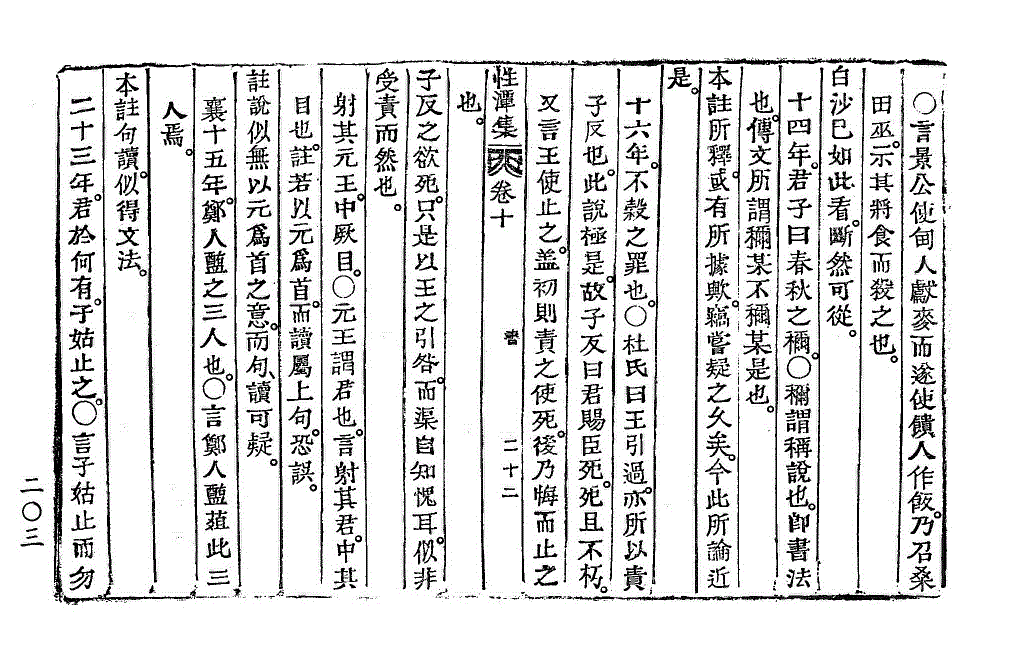 ○言景公使甸人献麦而遂使馈人作饭。乃召桑田巫。示其将食而杀之也。
○言景公使甸人献麦而遂使馈人作饭。乃召桑田巫。示其将食而杀之也。白沙已如此看。断然可从。
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称谓称说也。即书法也。传文所谓称某不称某是也。
本注所释。或有所据欤。窃尝疑之久矣。今此所论近是。
十六年。不谷之罪也。○杜氏曰王引过。亦所以责子反也。此说极是。故子反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又言王使止之。盖初则责之使死。后乃悔而止之也。
子反之欲死。只是以王之引咎。而渠自知愧耳。似非受责而然也。
射其元王。中厥目。○元王谓君也。言射其君。中其目也。注若以元为首。而读属上句。恐误。
注说似无以元为首之意。而句读可疑。
襄十五年。郑人醢之三人也。○言郑人醢菹此三人焉。
本注句读。似得文法。
二十三年。君于何有。子姑止之。○言子姑止而勿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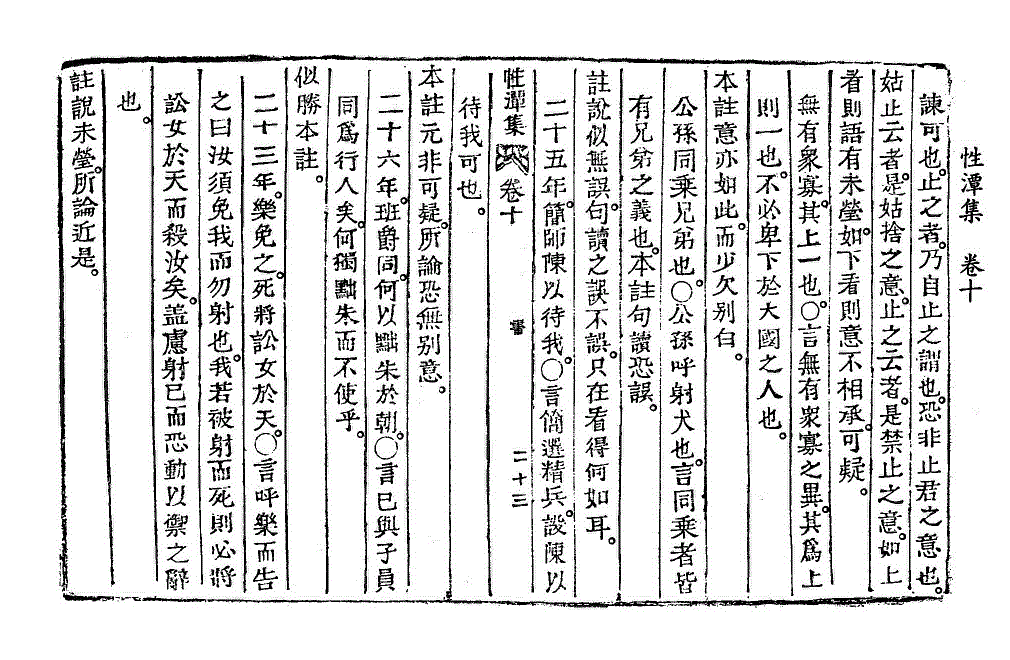 谏可也。止之者。乃自止之谓也。恐非止君之意也。
谏可也。止之者。乃自止之谓也。恐非止君之意也。姑止云者。是姑舍之意。止之云者。是禁止之意。如上看则语有未莹。如下看则意不相承。可疑。
无有众寡。其上一也。○言无有众寡之异。其为上则一也。不必卑下于大国之人也。
本注意亦如此。而少欠别白。
公孙同乘兄弟也。○公孙呼射犬也。言同乘者皆有兄弟之义也。本注句读恐误。
注说似无误。句读之误不误。只在看得何如耳。
二十五年。简师陈以待我。○言简选精兵。设陈以待我可也。
本注元非可疑。所论恐无别意。
二十六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言已与子员同为行人矣。何独黜朱而不使乎。
似胜本注。
二十三年。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言呼乐而告之曰汝须免我而勿射也。我若被射而死则必将讼女于天而杀汝矣。盖虑射己而恐动以御之辞也。
注说未莹。所论近是。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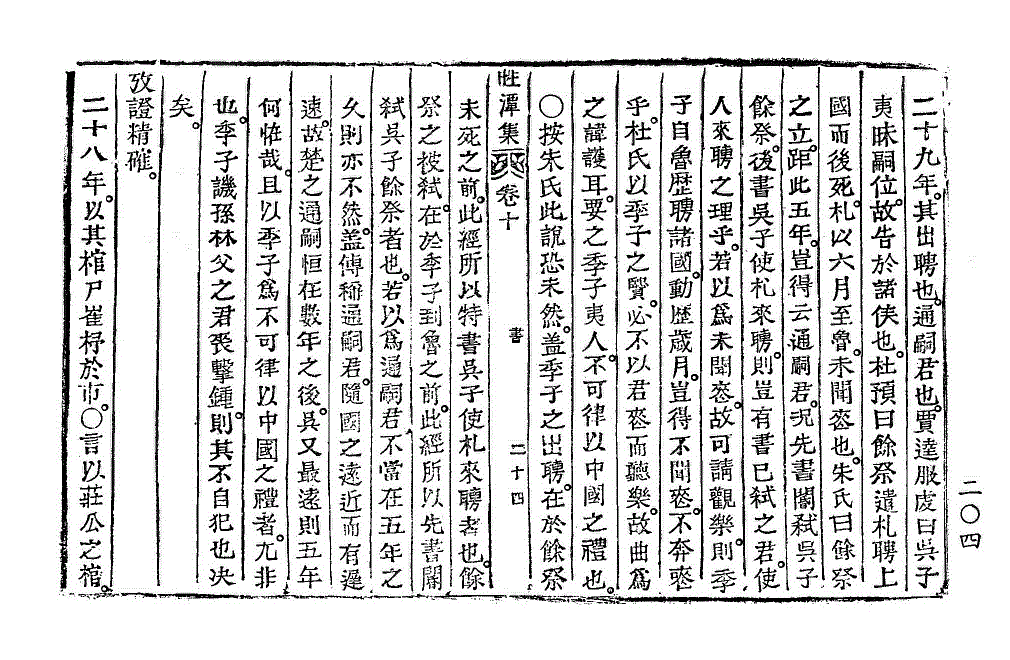 二十九年。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贾逵服虔曰吴子夷昧嗣位。故告于诸侯也。杜预曰馀祭遣札聘上国而后死。札以六月至鲁。未闻丧也。朱氏曰馀祭之立。距此五年。岂得云通嗣君。况先书阍弑吴子馀祭。后书吴子使札来聘。则岂有书已弑之君。使人来聘之理乎。若以为未闻丧。故可请观乐。则季子自鲁历聘诸国。动历岁月。岂得不闻丧。不奔丧乎。杜氏以季子之贤。必不以君丧而听乐。故曲为之讳护耳。要之季子夷人。不可律以中国之礼也。○按朱氏此说恐未然。盖季子之出聘。在于馀祭未死之前。此经所以特书吴子使札来聘者也。馀祭之被弑。在于季子到鲁之前。此经所以先书阍弑吴子馀祭者也。若以为通嗣君不当在五年之久则亦不然。盖传称通嗣君。随国之远近而有迟速。故楚之通嗣恒在数年之后。吴又最远则五年何怪哉。且以季子为不可律以中国之礼者。尤非也。季子讥孙林父之君丧击钟。则其不自犯也决矣。
二十九年。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贾逵服虔曰吴子夷昧嗣位。故告于诸侯也。杜预曰馀祭遣札聘上国而后死。札以六月至鲁。未闻丧也。朱氏曰馀祭之立。距此五年。岂得云通嗣君。况先书阍弑吴子馀祭。后书吴子使札来聘。则岂有书已弑之君。使人来聘之理乎。若以为未闻丧。故可请观乐。则季子自鲁历聘诸国。动历岁月。岂得不闻丧。不奔丧乎。杜氏以季子之贤。必不以君丧而听乐。故曲为之讳护耳。要之季子夷人。不可律以中国之礼也。○按朱氏此说恐未然。盖季子之出聘。在于馀祭未死之前。此经所以特书吴子使札来聘者也。馀祭之被弑。在于季子到鲁之前。此经所以先书阍弑吴子馀祭者也。若以为通嗣君不当在五年之久则亦不然。盖传称通嗣君。随国之远近而有迟速。故楚之通嗣恒在数年之后。吴又最远则五年何怪哉。且以季子为不可律以中国之礼者。尤非也。季子讥孙林父之君丧击钟。则其不自犯也决矣。考證精确。
二十八年。以其棺尸崔杼于市。○言以庄公之棺。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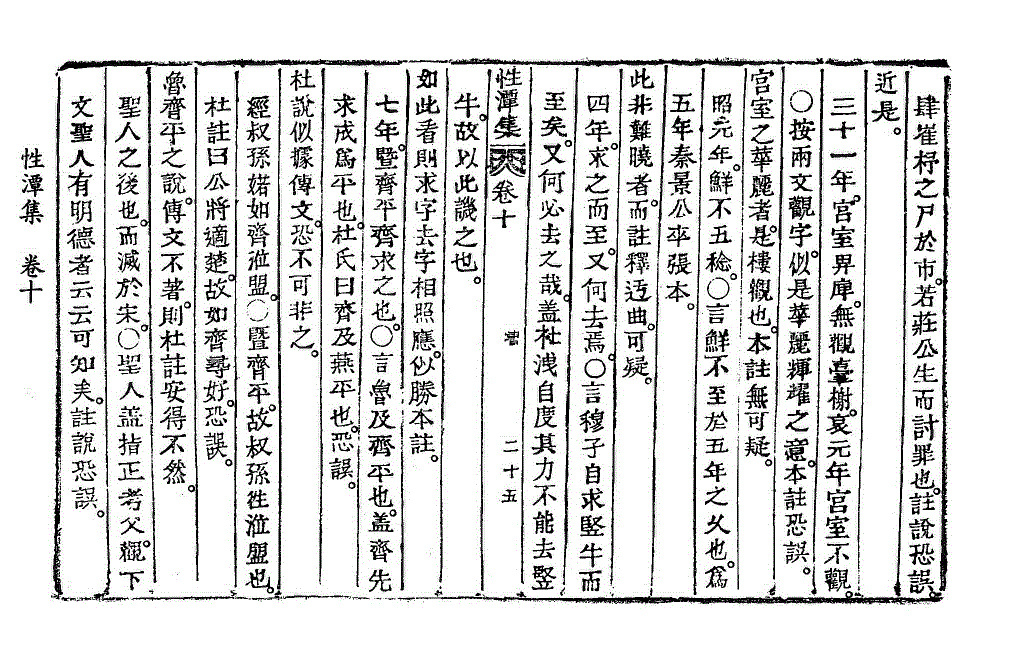 肆崔杼之尸于市。若庄公生而讨罪也。注说恐误。
肆崔杼之尸于市。若庄公生而讨罪也。注说恐误。近是。
三十一年。宫室畀庳。无观台榭。哀元年宫室不观。○按两文观字。似是华丽辉耀之意。本注恐误。
宫室之华丽者。是楼观也。本注无可疑。
昭元年。鲜不五稔。○言鲜不至于五年之久也。为五年秦景公卒张本。
此非难晓者。而注释迂曲。可疑。
四年。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穆子自求竖牛而至矣。又何必去之哉。盖杜泄自度其力不能去竖牛。故以此讥之也。
如此看则求字去字相照应。似胜本注。
七年。暨齐平齐求之也。○言鲁及齐平也。盖齐先求成为平也。杜氏曰齐及燕平也。恐误。
杜说似据传文。恐不可非之。
经叔孙婼如齐涖盟。○暨齐平。故叔孙往涖盟也。杜注曰公将适楚。故如齐寻好。恐误。
鲁齐平之说。传文不著。则杜注安得不然。
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圣人盖指正考父。观下文圣人有明德者云云可知矣。注说恐误。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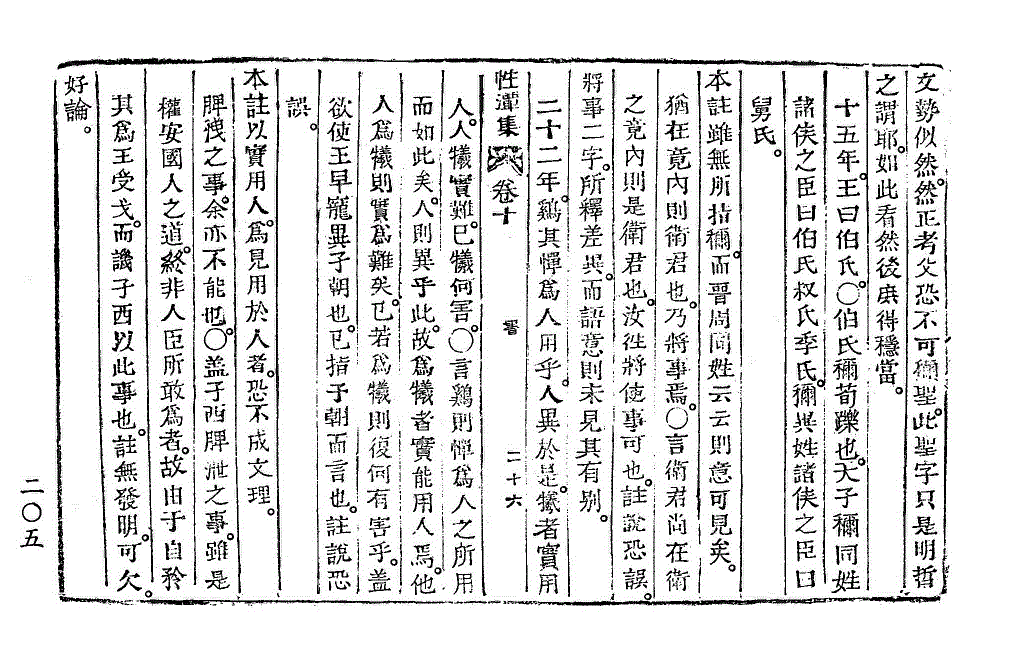 文势似然。然正考父恐不可称圣。此圣字只是明哲之谓耶。如此看然后庶得稳当。
文势似然。然正考父恐不可称圣。此圣字只是明哲之谓耶。如此看然后庶得稳当。十五年。王曰伯氏。○伯氏称荀跞也。天子称同姓诸侯之臣曰伯氏叔氏季氏。称异姓诸侯之臣曰舅氏。
本注虽无所指称。而晋周同姓云云则意可见矣。
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言卫君尚在卫之竟内则是卫君也。汝往将使事可也。注说恐误。
将事二字。所释差异。而语意则未见其有别。
二十二年。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言鸡则惮为人之所用而如此矣。人则异乎此。故为牺者实能用人焉。他人为牺则实为难矣。己若为牺则复何有害乎。盖欲使王早宠异子朝也。己指子朝而言也。注说恐误。
本注以实用人。为见用于人者。恐不成文理。
脾泄之事。余亦不能也。○盖子西脾泄之事。虽是权安国人之道。终非人臣所敢为者。故由于自矜其为王受戈。而讥子西以此事也。注无发明。可欠。
好论。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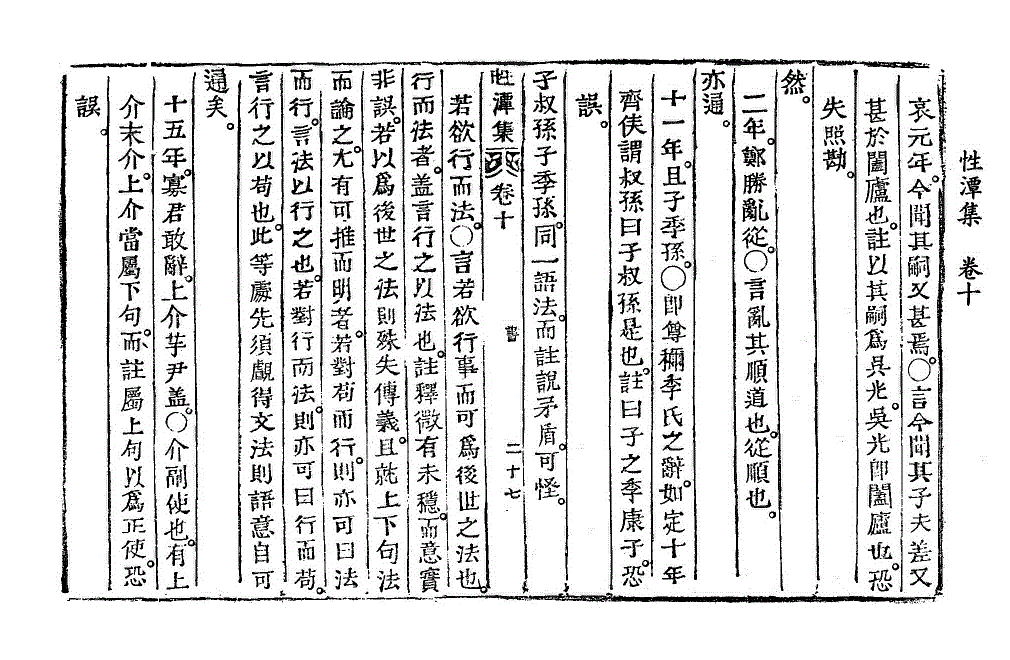 哀元年。今闻其嗣又甚焉。○言今闻其子夫差又甚于阖庐也。注以其嗣为吴光。吴光即阖庐也。恐失照勘。
哀元年。今闻其嗣又甚焉。○言今闻其子夫差又甚于阖庐也。注以其嗣为吴光。吴光即阖庐也。恐失照勘。然。
二年。郑胜乱从。○言乱其顺道也。从顺也。
亦通。
十一年。且子季孙。○即尊称季氏之辞。如定十年齐侯谓叔孙曰子叔孙是也。注曰子之季康子。恐误。
子叔孙子季孙。同一语法。而注说矛盾。可怪。
若欲行而法。○言若欲行事而可为后世之法也。
行而法者。盖言行之以法也。注释微有未稳。而意实非误。若以为后世之法则殊失传义。且就上下句法而论之。尤有可推而明者。若对苟而行。则亦可曰法而行。言法以行之也。若对行而法。则亦可曰行而苟。言行之以苟也。此等处先须觑得文法则语意自可通矣。
十五年。寡君敢辞。上介芋尹盖。○介副使也。有上介末介。上介当属下句。而注属上句以为正使。恐误。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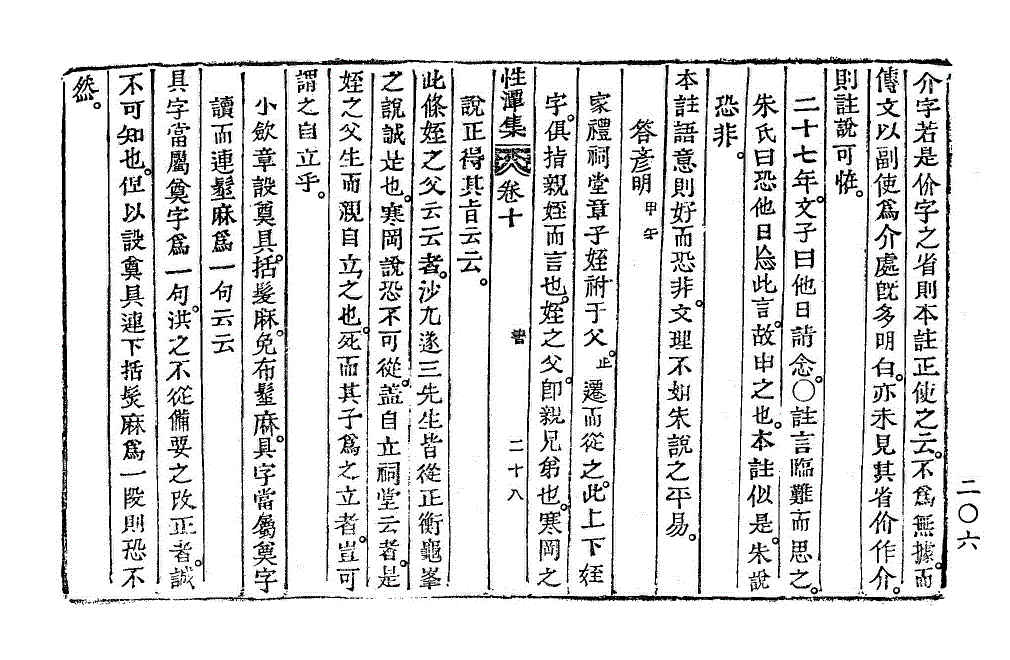 介字若是价字之省则本注正使之云。不为无据。而传文以副使为介处既多明白。亦未见其省价作介。则注说可怪。
介字若是价字之省则本注正使之云。不为无据。而传文以副使为介处既多明白。亦未见其省价作介。则注说可怪。二十七年。文子曰他日请念。○注言临难而思之。朱氏曰恐他日忘此言。故申之也。本注似是。朱说恐非。
本注语意则好而恐非。文理不如朱说之平易。
答彦明(甲午)
家礼祠堂章子侄祔于父。(止)迁而从之。此上下侄字。俱指亲侄而言也。侄之父。即亲兄弟也。寒冈之说正得其旨云云。
此条侄之父云云者。沙尤遂三先生皆从正衡龟峰之说诚是也。寒冈说恐不可从。盖自立祠堂云者。是侄之父生而亲自立之也。死而其子为之立者。岂可谓之自立乎。
小敛章设奠具。括发麻。免布髽麻。具字当属奠字读而连髽麻为一句云云。
具字当属奠字为一句。洪之不从备要之改正者。诚不可知也。但以设奠具连下括发麻为一段则恐不然。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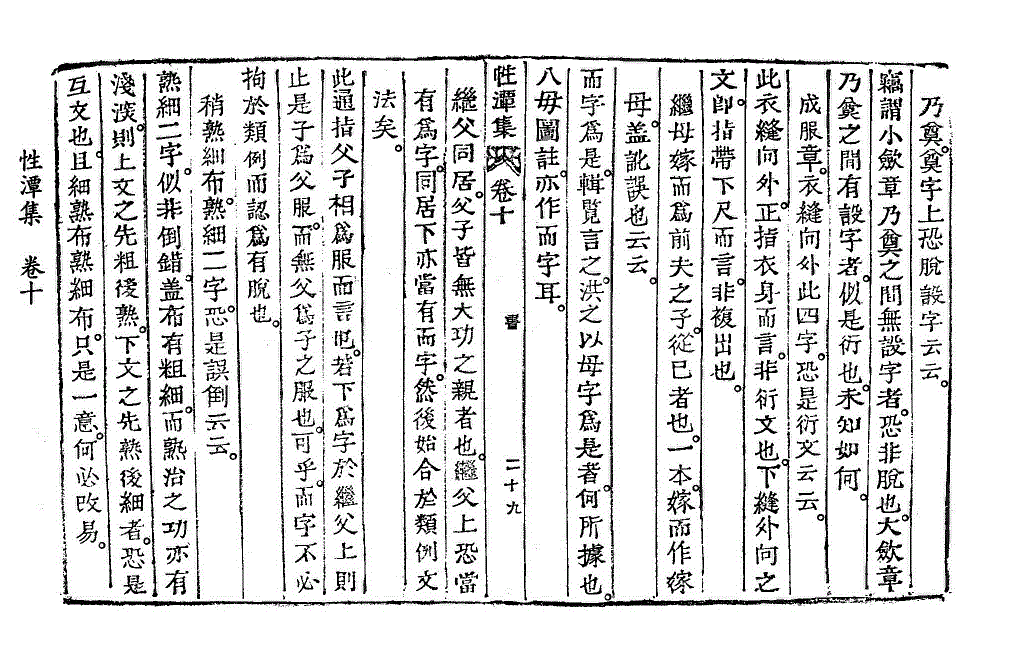 乃奠。奠字上恐脱设字云云。
乃奠。奠字上恐脱设字云云。窃谓小敛章乃奠之间无设字者。恐非脱也。大敛章乃奠之间有设字者。似是衍也。未知如何。
成服章。衣缝向外此四字。恐是衍文云云。
此衣缝向外。正指衣身而言。非衍文也。下缝外向之文。即指带下尺而言。非复出也。
继母嫁而为前夫之子。从己者也。一本。嫁而作嫁母。盖讹误也云云。
而字为是。辑览言之。洪之以母字为是者。何所据也。八母图注。亦作而字耳。
继父同居。父子皆无大功之亲者也。继父上恐当有为字。同居下亦当有而字。然后始合于类例文法矣。
此通指父子相为服而言也。若下为字于继父上则止是子为父服。而无父为子之服也。可乎。而字不必拘于类例而认为有脱也。
稍熟细布。熟细二字。恐是误倒云云。
熟细二字。似非倒错。盖布有粗细。而熟治之功亦有浅深。则上文之先粗后熟。下文之先熟后细者。恐是互文也。且细熟布熟细布。只是一意。何必改易。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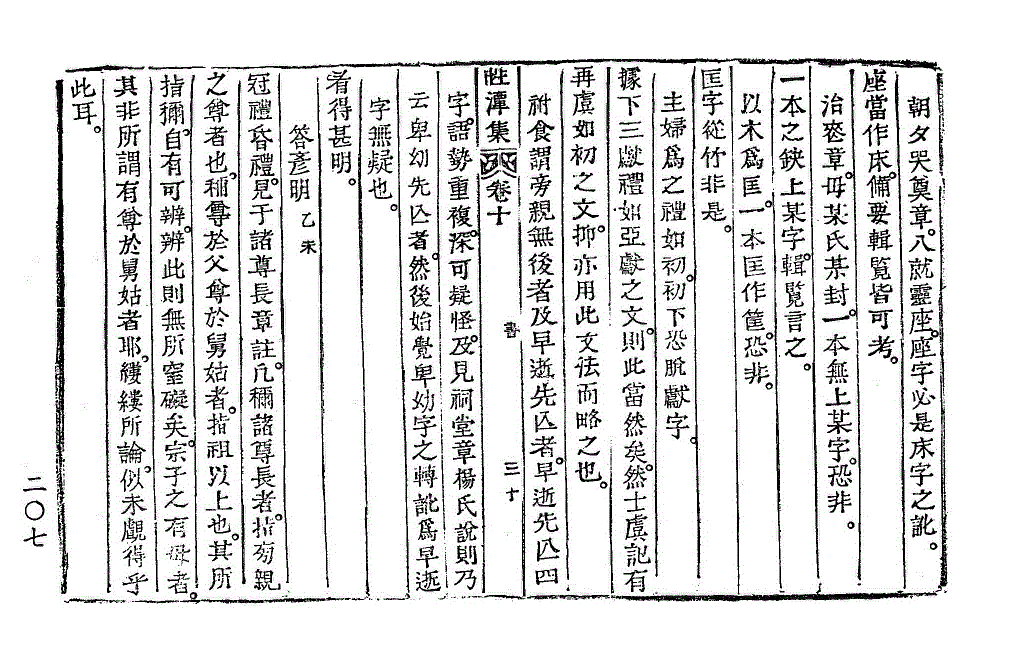 朝夕哭奠章。入就灵座。座字必是床字之讹。
朝夕哭奠章。入就灵座。座字必是床字之讹。座当作床。备要辑览皆可考。
治丧章。母某氏某封。一本无上某字。恐非。
一本之缺上某字。辑览言之。
以木为匡。一本匡作筐。恐非。
匡字从竹非是。
主妇为之礼如初。初下恐脱献字。
据下三献礼如亚献之文。则此当然矣。然士虞记有再虞如初之文。抑亦用此文法而略之也。
祔食谓旁亲无后者及早逝先亡者。早逝先亡四字。语势重复。深可疑怪。及见祠堂章杨氏说则乃云卑幼先亡者。然后始觉卑幼字之转讹为早逝字无疑也。
看得甚明。
答彦明(乙未)
冠礼昏礼。见于诸尊长章注。凡称诸尊长者。指旁亲之尊者也。称尊于父尊于舅姑者。指祖以上也。其所指称。自有可辨。辨此则无所窒碍矣。宗子之有母者。其非所谓有尊于舅姑者耶。缕缕所论。似未觑得乎此耳。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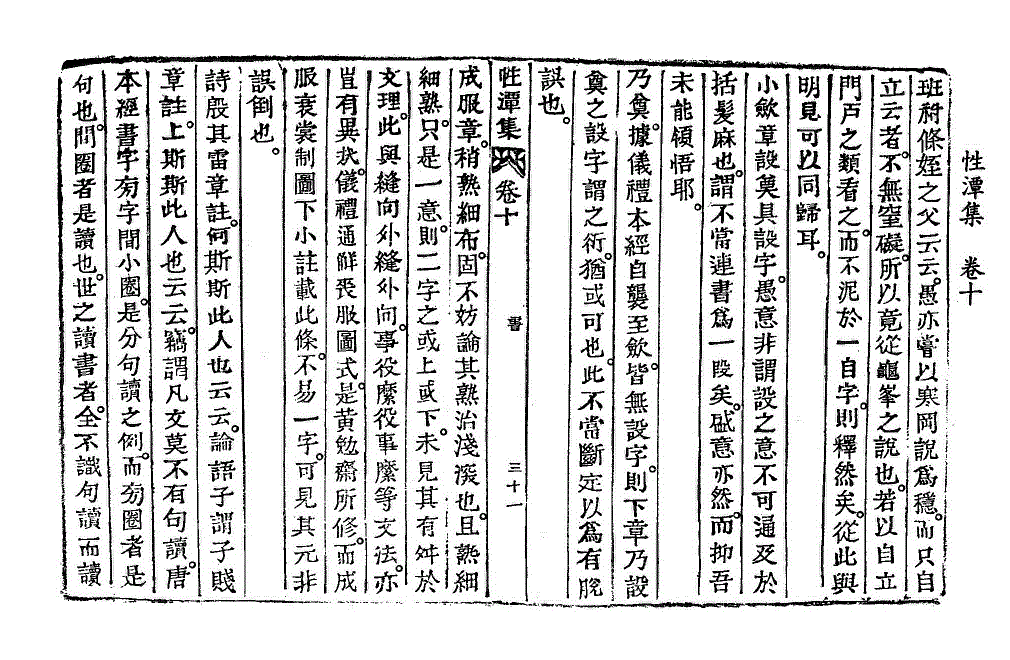 班祔条侄之父云云。愚亦尝以寒冈说为稳。而只自立云者。不无窒碍。所以竟从龟峰之说也。若以自立门户之类看之。而不泥于一自字。则释然矣。从此与明见可以同归耳。
班祔条侄之父云云。愚亦尝以寒冈说为稳。而只自立云者。不无窒碍。所以竟从龟峰之说也。若以自立门户之类看之。而不泥于一自字。则释然矣。从此与明见可以同归耳。小敛章设奠具设字。愚意非谓设之意不可通及于括发麻也。谓不当连书为一段矣。盛意亦然。而抑吾未能领悟耶。
乃奠。据仪礼本经自袭至敛。皆无设字。则下章乃设奠之设字谓之衍。犹或可也。此不当断定以为有脱误也。
成服章。稍熟细布。固不妨论其熟治浅深也。且熟细细熟。只是一意。则二字之或上或下。未见其有舛于文理。此与缝向外缝外向。事役縻役事縻等文法。亦岂有异哉。仪礼通解丧服图式。是黄勉斋所修。而成服衰裳制图下小注载此条。不易一字。可见其元非误倒也。
诗殷其雷章注。何斯斯此人也云云。论语子谓子贱章注。上斯斯此人也云云。窃谓凡文莫不有句读。唐本经书字旁字间小圈。是分句读之例。而旁圈者是句也。间圈者是读也。世之读书者。全不识句读而读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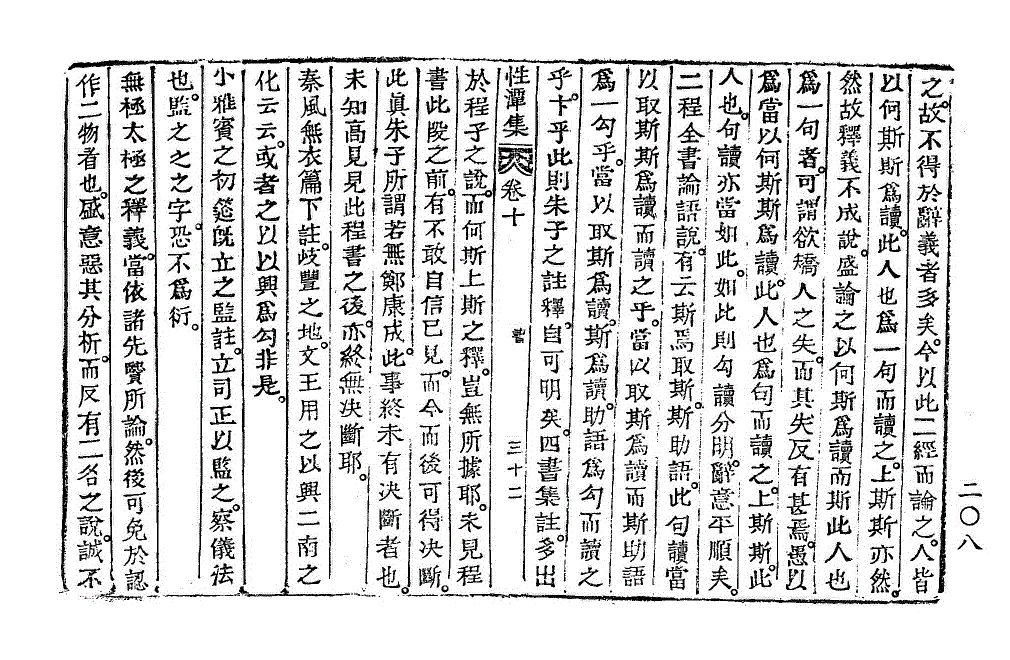 之。故不得于辞义者多矣。今以此二经而论之。人皆以何斯斯为读。此人也为一句而读之。上斯斯亦然。然故释义不成说。盛论之以何斯为读而斯此人也为一句者。可谓欲矫人之失。而其失反有甚焉。愚以为当以何斯斯为读。此人也为句而读之。上斯斯。此人也。句读亦当如此。如此则勾读分明。辞意平顺矣。二程全书论语说。有云斯焉取斯。斯助语。此句读当以取斯斯为读而读之乎。当以取斯为读而斯助语为一勾乎。当以取斯为读。斯为读。助语为勾而读之乎。卞乎此则朱子之注释。自可明矣。四书集注。多出于程子之说。而何斯上斯之释。岂无所据耶。未见程书此段之前。有不敢自信己见。而今而后可得决断。此真朱子所谓若无郑康成。此事终未有决断者也。未知高见见此程书之后。亦终无决断耶。
之。故不得于辞义者多矣。今以此二经而论之。人皆以何斯斯为读。此人也为一句而读之。上斯斯亦然。然故释义不成说。盛论之以何斯为读而斯此人也为一句者。可谓欲矫人之失。而其失反有甚焉。愚以为当以何斯斯为读。此人也为句而读之。上斯斯。此人也。句读亦当如此。如此则勾读分明。辞意平顺矣。二程全书论语说。有云斯焉取斯。斯助语。此句读当以取斯斯为读而读之乎。当以取斯为读而斯助语为一勾乎。当以取斯为读。斯为读。助语为勾而读之乎。卞乎此则朱子之注释。自可明矣。四书集注。多出于程子之说。而何斯上斯之释。岂无所据耶。未见程书此段之前。有不敢自信己见。而今而后可得决断。此真朱子所谓若无郑康成。此事终未有决断者也。未知高见见此程书之后。亦终无决断耶。秦风无衣篇下注。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云云。或者之以以兴为勾非是。
小雅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注。立司正以监之。察仪法也。监之之之字。恐不为衍。
无极太极之释义。当依诸先贤所论。然后可免于认作二物看也。盛意恶其分析。而反有二名之说。诚不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9H 页
 可知也。二名云者。岂非所谓无极之外。复有太极者耶。
可知也。二名云者。岂非所谓无极之外。复有太极者耶。与三从弟诚夫(焕实○甲午)
郭生家禫事。何以为定耶。问解有二条。可据以参酌行之者。一则以为丧中既不可行禅。而过时又不可追行。诸父岂可以嫡孙之故而不脱服也。设位哭除恐当。一则以为父丧中不可参祖母禫。诸叔父告辞行之可也。此二条皆据承重主丧而言者。而上条则不许众子之行禫。下条则许其告辞行之矣。今郭生其主丧之长兄既死无嗣。则代之而主丧者。非渠而谁耶。虽使郭生有侄承重。既有告辞行之之文。则郭生之行禫。未为无据。而况既代其兄而主丧。则何可废禫事乎。
答诚夫
父在则为长子不服三年。盖周之道。有嫡子无嫡孙。嫡孙犹同庶孙之例也。此载问解矣。丧服不杖期条为嫡孙疏曰。嫡子死。其嫡孙承重者祖为之期。据此则祖之于孙。若嫡子在而非承重者则为之服当为大功之制也。三位之葬以品字形封坟者。其所祔恐当前配右而后配左矣。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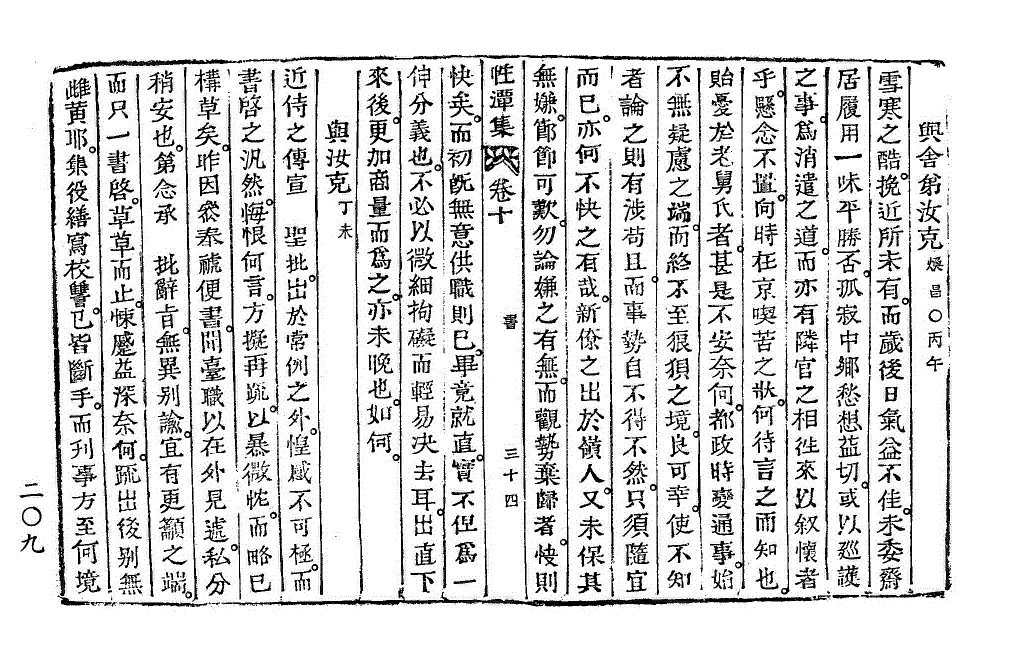 与舍弟汝克(焕昌○丙午)
与舍弟汝克(焕昌○丙午)雪寒之酷。挽近所未有。而岁后日气益不佳。未委斋居履用一味平胜否。孤寂中乡愁想益切。或以巡护之事。为消遣之道。而亦有邻官之相往来以叙怀者乎。悬念不置。向时在京吃苦之状。何待言之而知也。贻忧于老舅氏者。甚是不安奈何。都政时变通事。始不无疑虑之端。而终不至狼狈之境。良可幸。使不知者论之则有涉苟且。而事势自不得不然。只须随宜而已。亦何不快之有哉。新僚之出于岭人。又未保其无嫌。节节可叹。勿论嫌之有无。而观势弃归者。快则快矣。而初既无意供职则已。毕竟就直。实不但为一伸分义也。不必以微细拘碍而轻易决去耳。出直下来后。更加商量而为之。亦未晚也。如何。
与汝克(丁未)
近侍之传宣 圣批。出于常例之外。惶感不可极。而书启之汎然。悔恨何言。方拟再疏。以暴微忱。而略已构草矣。昨因参奉褫便书。闻台职以在外见递。私分稍安也。第念承 批辞旨。无异别谕。宜有更吁之端。而只一书启。草草而止。悚蹙益深奈何。疏出后别无雌黄耶。集役缮写校雠。已皆断手。而刊事方至何境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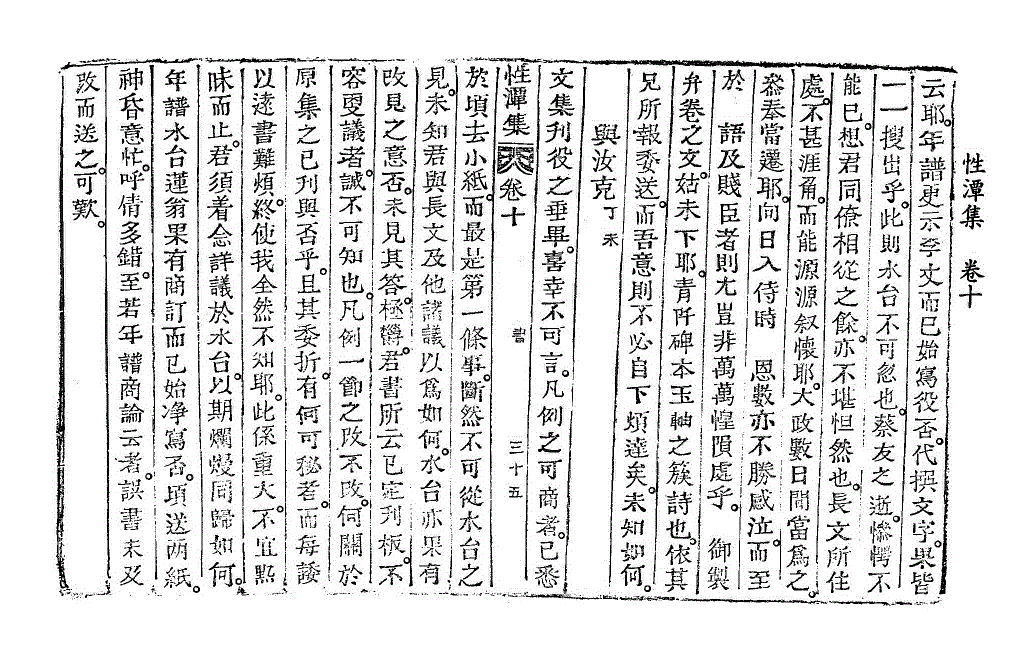 云耶。年谱更示李丈而已始写役否。代撰文字。果皆一一搜出乎。此则水台不可忽也。蔡友之逝。惨愕不能已。想君同僚相从之馀。亦不堪怛然也。长文所住处。不甚涯角。而能源源叙怀耶。大政数日间当为之。参奉当迁耶。向日入侍时 恩数亦不胜感泣。而至于 语及贱臣者则尤岂非万万惶陨处乎。 御制弁卷之文。姑未下耶。青阡碑本玉轴之簇诗也。依其兄所报委送。而吾意则不必自下烦达矣。未知如何。
云耶。年谱更示李丈而已始写役否。代撰文字。果皆一一搜出乎。此则水台不可忽也。蔡友之逝。惨愕不能已。想君同僚相从之馀。亦不堪怛然也。长文所住处。不甚涯角。而能源源叙怀耶。大政数日间当为之。参奉当迁耶。向日入侍时 恩数亦不胜感泣。而至于 语及贱臣者则尤岂非万万惶陨处乎。 御制弁卷之文。姑未下耶。青阡碑本玉轴之簇诗也。依其兄所报委送。而吾意则不必自下烦达矣。未知如何。与汝克(丁未)
文集刊役之垂毕。喜幸不可言。凡例之可商者。已悉于顷去小纸。而最是第一条事。断然不可从水台之见。未知君与长文及他诸议以为如何。水台亦果有改见之意否。未见其答。极郁。君书所云已定刊板。不容更议者。诚不可知也。凡例一节之改不改。何关于原集之已刊与否乎。且其委折。有何可秘者。而每诿以远书难烦。终使我全然不知耶。此系重大。不宜䵝昧而止。君须着念详议于水台。以期烂熳同归如何。年谱水台莲翁果有商订而已始净写否。顷送两纸。神昏意忙。呼倩多错。至若年谱商论云者。误书未及改而送之。可叹。
答汝克
奉事骊行便所付手滋慰甚。日间雨雪连仍。旅况一味否。悬恋无已。骊院碑文之下。感泣罔涯。而至于奉事之承 命陪奉而来。尤是 恩数之有出寻常。吾辈糜粉图报之忱。当复如何哉。第阖族穷拙。无以济济趋会于竖碑之时。若负 圣眷。举切闷蹙而已。谱事携贰之端。何以归宿耶。远莫之详。泄泄不可言。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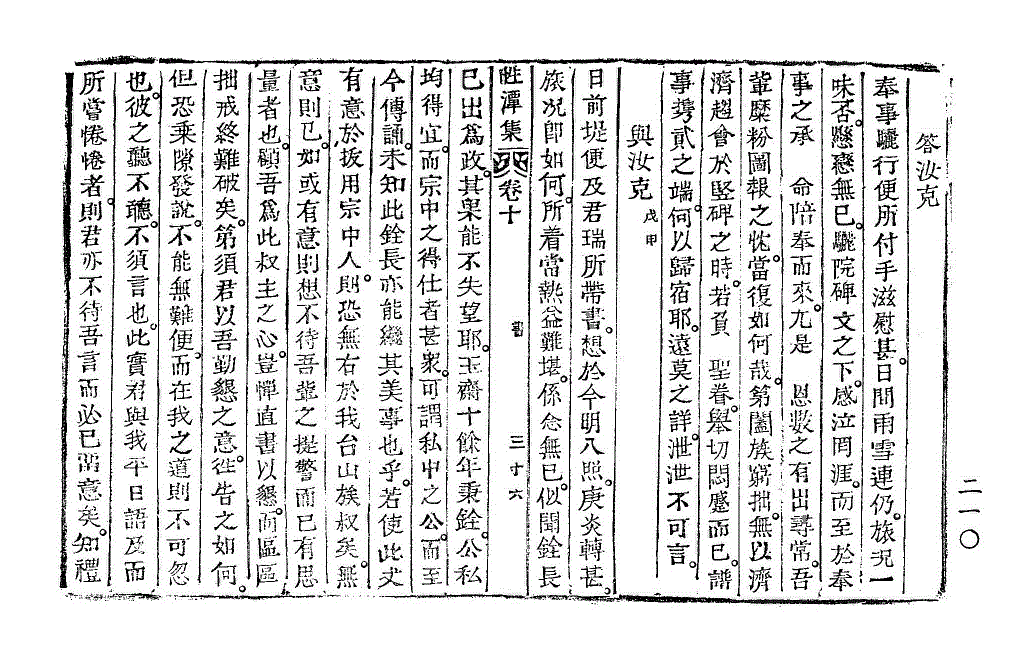 与汝克(戊申)
与汝克(戊申)日前堤便及君瑞所带书。想于今明入照。庚炎转甚。旅况即如何。所着当热益难堪。系念无已。似闻铨长已出为政。其果能不失望耶。玉斋十馀年秉铨。公私均得宜。而宗中之得仕者甚众。可谓私中之公。而至今传诵。未知此铨长亦能继其美事也乎。若使此丈有意于拔用宗中人。则恐无右于我台山族叔矣。无意则已。如或有意则想不待吾辈之提警而已有思量者也。顾吾为此叔主之心。岂惮直书以恳。而区区拙戒终难破矣。第须君以吾勤恳之意。往告之如何。但恐乘隙发说。不能无难便。而在我之道则不可忽也。彼之听不听。不须言也。此实君与我平日语及而所尝惓惓者。则君亦不待吾言而必已留意矣。知礼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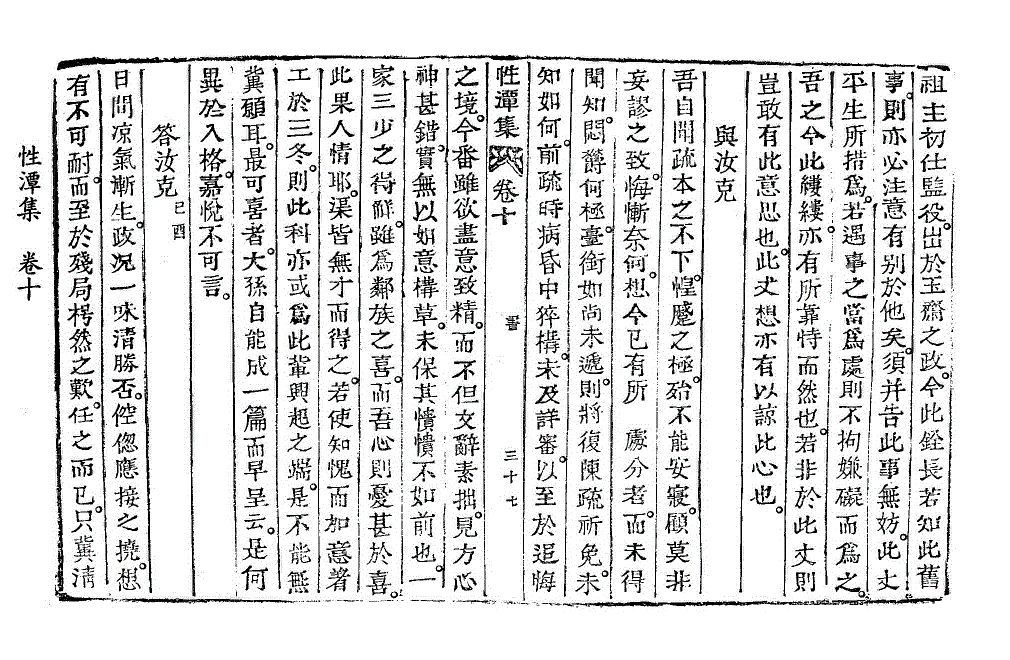 祖主初仕监役。出于玉斋之政。今此铨长若知此旧事。则亦必注意有别于他矣。须并告此事无妨。此丈平生所措为。若遇事之当为处则不拘嫌碍而为之。吾之今此缕缕。亦有所靠恃而然也。若非于此丈则岂敢有此意思也。此丈想亦有以谅此心也。
祖主初仕监役。出于玉斋之政。今此铨长若知此旧事。则亦必注意有别于他矣。须并告此事无妨。此丈平生所措为。若遇事之当为处则不拘嫌碍而为之。吾之今此缕缕。亦有所靠恃而然也。若非于此丈则岂敢有此意思也。此丈想亦有以谅此心也。与汝克
吾自闻疏本之不下。惶蹙之极。殆不能安寝。顾莫非妄谬之致。悔惭奈何。想今已有所 处分者。而未得闻知。闷郁何极。台衔如尚未递。则将复陈疏祈免。未知如何。前疏时病昏中猝构。未及详审。以至于追悔之境。今番虽欲尽意致精。而不但文辞素拙。见方心神甚错。实无以如意构草。未保其愦愦不如前也。一家三少之得解。虽为邻族之喜。而吾心则忧甚于喜。此果人情耶。渠皆无才而得之。若使知愧而加意着工于三冬。则此科亦或为此辈兴起之端。是不能无冀愿耳。最可喜者。大孙自能成一篇而早呈云。是何异于入格。嘉悦不可言。
答汝克(己酉)
日间凉气渐生。政况一味清胜否。倥偬应接之挠。想有不可耐。而至于残局枵然之叹。任之而已。只冀清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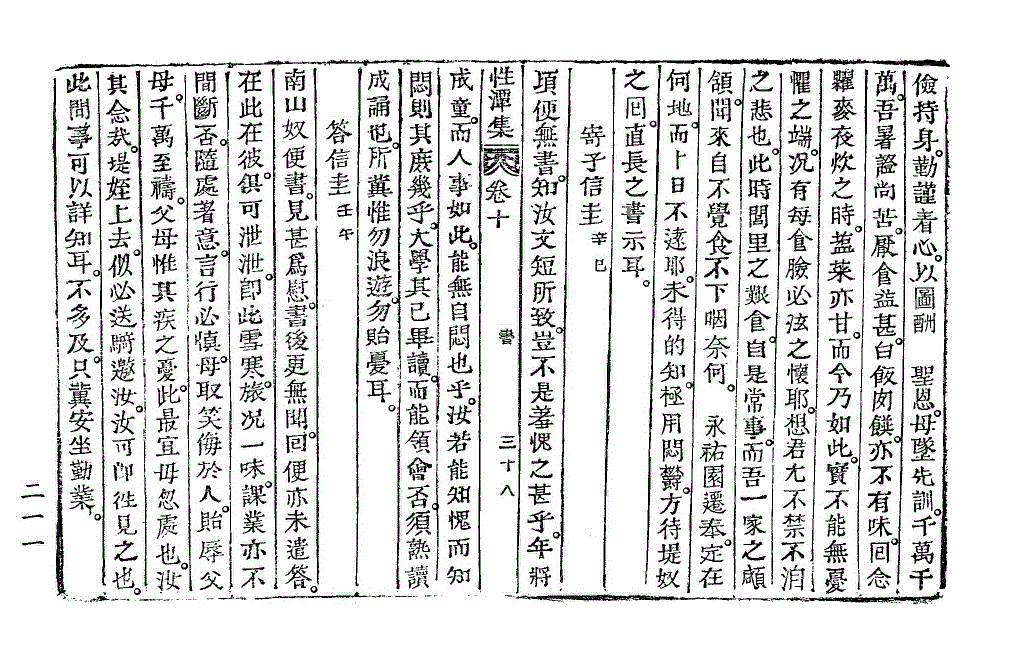 俭持身。勤谨着心。以图酬 圣恩。毋坠先训。千万千万。吾暑證尚苦。厌食益甚。白饭肉馔。亦不有味。回念粜麦夜炊之时。盐菜亦甘。而今乃如此。实不能无忧惧之端。况有每食脸必泫之怀耶。想君尤不禁不洎之悲也。此时闾里之艰食。自是常事。而吾一家之顑颔。闻来自不觉食不下咽奈何。 永祐园迁奉。定在何地。而卜日不远耶。未得的知。极用闷郁。方待堤奴之回。直长之书示耳。
俭持身。勤谨着心。以图酬 圣恩。毋坠先训。千万千万。吾暑證尚苦。厌食益甚。白饭肉馔。亦不有味。回念粜麦夜炊之时。盐菜亦甘。而今乃如此。实不能无忧惧之端。况有每食脸必泫之怀耶。想君尤不禁不洎之悲也。此时闾里之艰食。自是常事。而吾一家之顑颔。闻来自不觉食不下咽奈何。 永祐园迁奉。定在何地。而卜日不远耶。未得的知。极用闷郁。方待堤奴之回。直长之书示耳。寄子信圭(辛巳)
顷便无书。知汝文短所致。岂不是羞愧之甚乎。年将成童。而人事如此。能无自闷也乎。汝若能知愧而知闷则其庶几乎。大学其已毕读。而能领会否。须熟读成诵也。所冀惟勿浪游。勿贻忧耳。
答信圭(壬午)
南山奴便书。见甚为慰。书后更无闻。回便亦未遣答。在此在彼。俱可泄泄。即此雪寒。旅况一味。课业亦不间断否。随处着意。言行必慎。毋取笑侮于人。贻辱父母。千万至祷。父母惟其疾之忧。此最宜毋忽处也。汝其念哉。堤侄上去。似必送骑邀汝。汝可即往见之也。此间事可以详知耳。不多及。只冀安坐勤业。
寄信圭兼示申从钟秀(甲申)
夜间读况如何。信则熟读。大则课学否。大之所课卷匪久讫工。信可继受。而初卷则大可始之也。吾归似在旬间。其前须勿悠泛。周召南必成诵以待。得免墙面立也。所望于汝辈者。此一事而已。复有何说哉。在八卦亭灯下胡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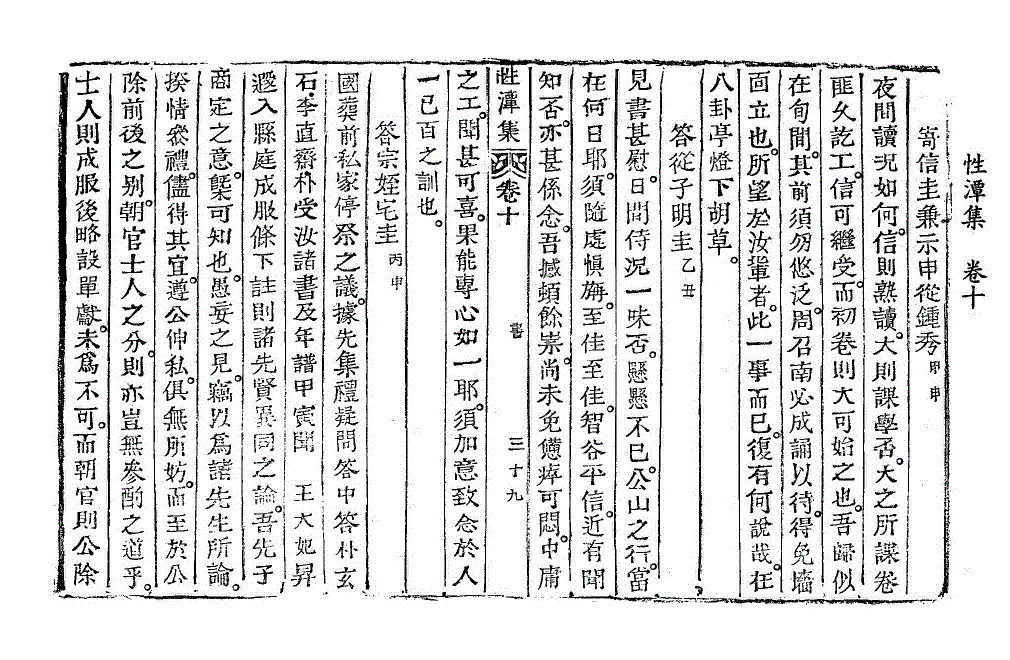 答从子明圭(乙丑)
答从子明圭(乙丑)见书甚慰。日间侍况一味否。悬悬不已。公山之行。当在何日耶。须随处慎旃。至佳至佳。智谷平信。近有闻知否。亦甚系念。吾撼顿馀祟。尚未免惫瘁可闷。中庸之工。闻甚可喜。果能专心如一耶。须加意致念于人一己百之训也。
答宗侄宅圭(丙申)
国葬前私家停祭之议。据先集礼疑问答中答朴玄石,李直斋,朴受汝诸书及年谱甲寅闻 王大妃升遐入县庭成服条下注则诸先贤异同之论。吾先子商定之意。槩可知也。愚妄之见。窃以为诸先生所论。揆情参礼。尽得其宜。遵公伸私。俱无所妨。而至于公除前后之别。朝官士人之分。则亦岂无参酌之道乎。士人则成服后略设单献。未为不可。而朝官则公除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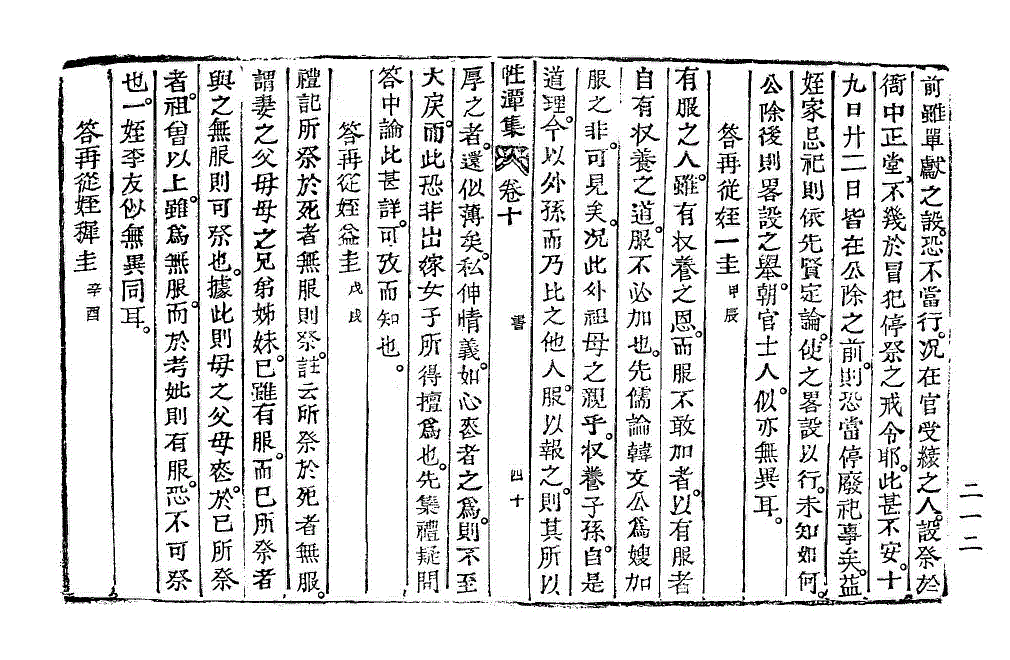 前虽单献之设。恐不当行。况在官受缞之人。设祭于衙中正堂。不几于冒犯停祭之戒令耶。此甚不安。十九日廿二日皆在公除之前。则恐当停废祀事矣。益侄家忌祀则依先贤定论。使之略设以行。未知如何。公除后则略设之举。朝官士人。似亦无异耳。
前虽单献之设。恐不当行。况在官受缞之人。设祭于衙中正堂。不几于冒犯停祭之戒令耶。此甚不安。十九日廿二日皆在公除之前。则恐当停废祀事矣。益侄家忌祀则依先贤定论。使之略设以行。未知如何。公除后则略设之举。朝官士人。似亦无异耳。答再从侄一圭(甲辰)
有服之人。虽有收养之恩。而服不敢加者。以有服者自有收养之道。服不必加也。先儒论韩文公为嫂加服之非。可见矣。况此外祖母之亲乎。收养子孙。自是道理。今以外孙而乃比之他人。服以报之。则其所以厚之者。还似薄矣。私伸情义。如心丧者之为。则不至大戾。而此恐非出嫁女子所得擅为也。先集礼疑问答中论此甚详。可考而知也。
答再从侄益圭(戊戌)
礼记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注云所祭于死者无服。谓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己虽有服。而己所祭者与之无服则可祭也。据此则母之父母丧。于己所祭者。祖曾以上。虽为无服。而于考妣则有服。恐不可祭也。一侄李友似无异同耳。
答再从侄稚圭(辛酉)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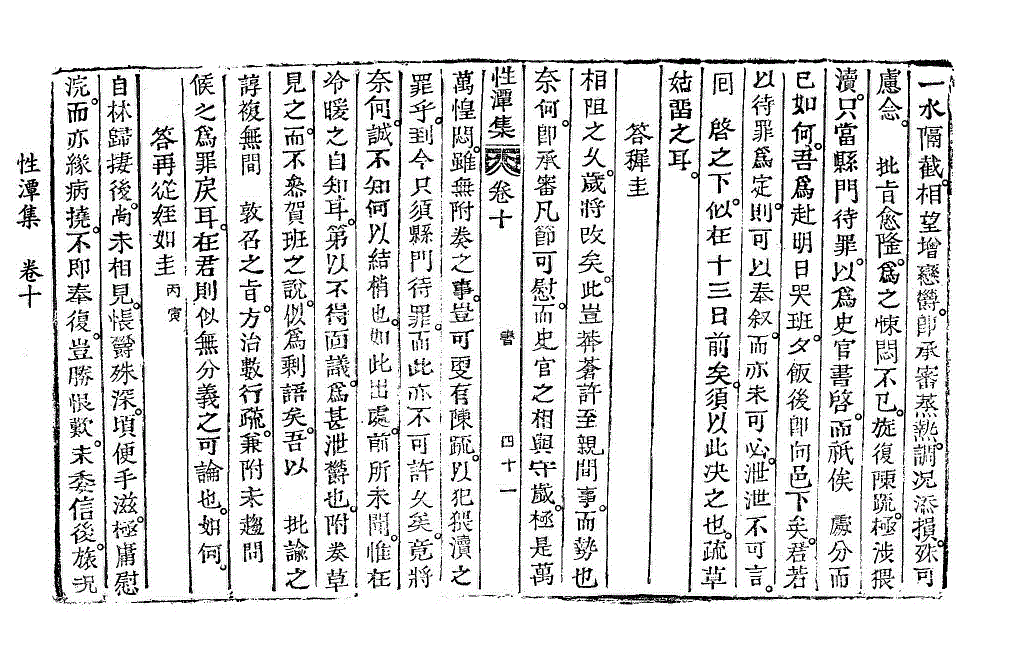 一水隔截。相望增恋郁。即承审蒸热。调况添损。殊可虑念。 批旨愈隆。为之悚闷不已。旋复陈疏。极涉猥渎。只当县门待罪。以为史官书启。而祇俟 处分而已如何。吾为赴明日哭班。夕饭后即向邑下矣。君若以待罪为定。则可以奉叙。而亦未可必。泄泄不可言。回 启之下。似在十三日前矣。须以此决之也。疏草姑留之耳。
一水隔截。相望增恋郁。即承审蒸热。调况添损。殊可虑念。 批旨愈隆。为之悚闷不已。旋复陈疏。极涉猥渎。只当县门待罪。以为史官书启。而祇俟 处分而已如何。吾为赴明日哭班。夕饭后即向邑下矣。君若以待罪为定。则可以奉叙。而亦未可必。泄泄不可言。回 启之下。似在十三日前矣。须以此决之也。疏草姑留之耳。答稚圭
相阻之久。岁将改矣。此岂莽苍许至亲间事。而势也奈何。即承审凡节可慰。而史官之相与守岁。极是万万惶闷。虽无附奏之事。岂可更有陈疏。以犯猥渎之罪乎。到今只须县门待罪。而此亦不可许久矣。竟将奈何。诚不知何以结梢也。如此出处。前所未闻。惟在冷暖之自知耳。第以不得面议。为甚泄郁也。附奏草见之。而不参贺班之说。似为剩语矣。吾以 批谕之谆复无间 敦召之旨。方治数行疏。兼附未趋问 候之为罪戾耳。在君则似无分义之可论也。如何。
答再从侄如圭(丙寅)
自林归栖后。尚未相见。怅郁殊深。顷便手滋。极庸慰浣。而亦缘病挠。不即奉复。岂胜恨叹。未委信后。旅况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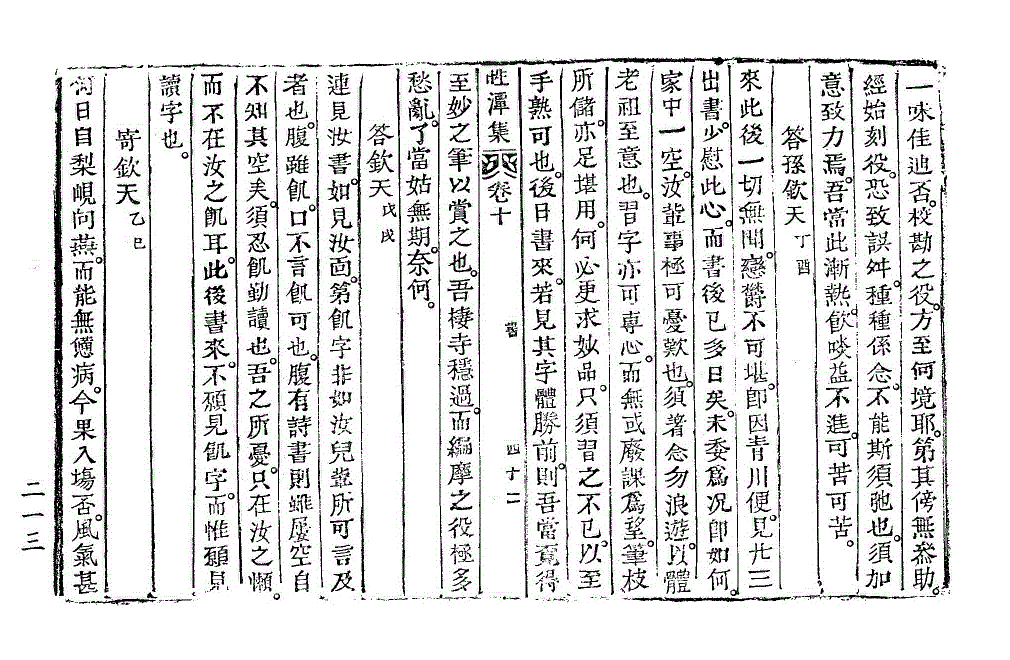 一味佳迪否。校勘之役。方至何境耶。第其傍无参助。经始刻役。恐致误舛。种种系念。不能斯须弛也。须加意致力焉。吾当此渐热。饮啖益不进。可苦可苦。
一味佳迪否。校勘之役。方至何境耶。第其傍无参助。经始刻役。恐致误舛。种种系念。不能斯须弛也。须加意致力焉。吾当此渐热。饮啖益不进。可苦可苦。答孙钦天(丁酉)
来此后一切无闻。恋郁不可堪。即因青川便。见廿三出书。少慰此心。而书后已多日矣。未委为况即如何。家中一空。汝辈事极可忧叹也。须着念勿浪游。以体老祖至意也。习字亦可专心。而无或废课为望。笔枝所储。亦足堪用。何必更求妙品。只须习之不已。以至手熟可也。后日书来。若见其字体胜前。则吾当觅得至妙之笔以赏之也。吾栖寺稳过。而编摩之役极多愁乱。了当姑无期。奈何。
答钦天(戊戌)
连见汝书。如见汝面。第饥字非如汝儿辈所可言及者也。腹虽饥。口不言饥可也。腹有诗书则虽屡空自不知其空矣。须忍饥勤读也。吾之所忧。只在汝之懒。而不在汝之饥耳。此后书来。不愿见饥字。而惟愿见读字也。
寄钦天(乙巳)
何日自梨岘向燕。而能无惫病。今果入场否。风气甚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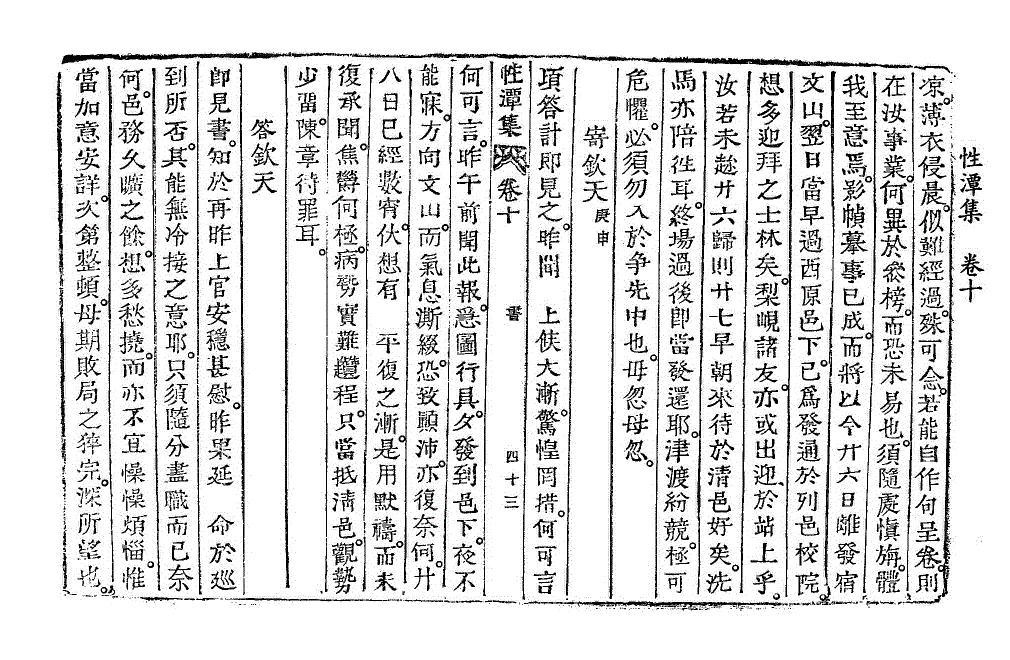 凉。薄衣侵晨。似难经过。殊可念。若能自作句呈卷。则在汝事业。何异于参榜。而恐未易也。须随处慎旃。体我至意焉。影帧摹事已成。而将以今廿六日离发宿文山。翌日当早过西原邑下。已为发通于列邑校院。想多迎拜之士林矣。梨岘诸友。亦或出迎于站上乎。汝若未趁廿六归则廿七早朝来待于清邑好矣。洗马亦陪往耳。终场过后即当发还耶。津渡纷竞。极可危惧。必须勿入于争先中也。毋忽毋忽。
凉。薄衣侵晨。似难经过。殊可念。若能自作句呈卷。则在汝事业。何异于参榜。而恐未易也。须随处慎旃。体我至意焉。影帧摹事已成。而将以今廿六日离发宿文山。翌日当早过西原邑下。已为发通于列邑校院。想多迎拜之士林矣。梨岘诸友。亦或出迎于站上乎。汝若未趁廿六归则廿七早朝来待于清邑好矣。洗马亦陪往耳。终场过后即当发还耶。津渡纷竞。极可危惧。必须勿入于争先中也。毋忽毋忽。寄钦天(庚申)
顷答计即见之。昨闻 上候大渐。惊惶罔措。何可言何可言。昨午前闻此报。急图行具。夕发到邑下。夜不能寐。方向文山。而气息澌缀。恐致颠沛。亦复奈何。廿八日已经数宵。伏想有 平复之渐。是用默祷。而未复承闻。焦郁何极。病势实难趱程。只当抵清邑。观势少留。陈章待罪耳。
答钦天
即见书。知于再昨上官安稳甚慰。昨果延 命于巡到所否。其能无冷接之意耶。只须随分尽职而已奈何。邑务久旷之馀。想多愁挠。而亦不宜懆懆烦恼。惟当加意安详。次第整顿。毋期败局之猝完。深所望也。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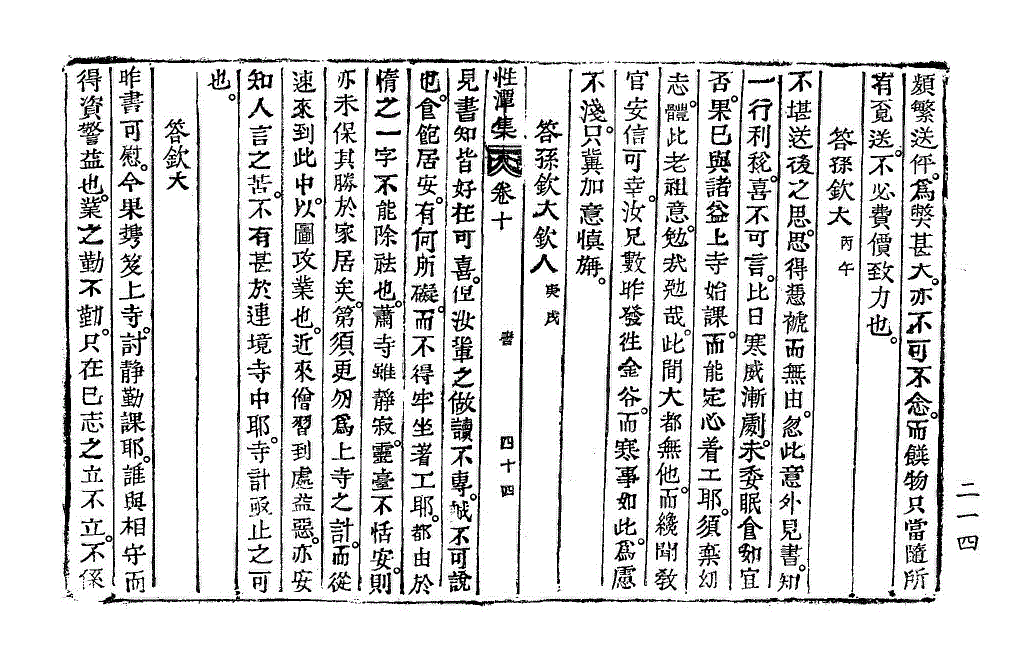 频繁送伻。为弊甚大。亦不可不念。而馔物只当随所有觅送。不必费价致力也。
频繁送伻。为弊甚大。亦不可不念。而馔物只当随所有觅送。不必费价致力也。答孙钦大(丙午)
不堪送后之思。思得凭褫而无由。忽此意外见书。知一行利税。喜不可言。比日寒威渐剧。未委眠食如宜否。果已与诸益上寺始课。而能定心着工耶。须弃幼志。体此老祖意。勉哉勉哉。此间大都无他。而才闻教官安信可幸。汝兄数昨发往金谷。而寒事如此。为虑不浅。只冀加意慎旃。
答孙钦大钦人(庚戌)
见书知皆好在可喜。但汝辈之做读不专。诚不可说也。食饱居安。有何所碍。而不得牢坐着工耶。都由于惰之一字不能除祛也。萧寺虽静寂。灵台不恬安。则亦未保其胜于家居矣。第须更勿为上寺之计。而从速来到此中。以图攻业也。近来僧习到处益恶。亦安知人言之苦。不有甚于连境寺中耶。寺计亟止之可也。
答钦大
昨书可慰。今果携笈上寺。讨静勤课耶。谁与相守而得资警益也。业之勤不勤。只在己志之立不立。不系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5H 页
 处所之静不静。须随处着工。毋为虚过三春也。第闻以衙客之出接于境内萧寺。不无人言。然则岂非不安之端。势须罢归。可知悉也。方以此意书报连衙。以为从速区处耳。吾依昨而辞疏尚未封进。亦可闷蹙。馀冀眠食如宜。做读不惰。
处所之静不静。须随处着工。毋为虚过三春也。第闻以衙客之出接于境内萧寺。不无人言。然则岂非不安之端。势须罢归。可知悉也。方以此意书报连衙。以为从速区处耳。吾依昨而辞疏尚未封进。亦可闷蹙。馀冀眠食如宜。做读不惰。答钦大(乙丑)
日前书见悉。知无挠抵达。而眷引均佳。欣慰无已。即日寒事益极。凡节更如何。悬念不置。吾姑如前㨾。而亦不无应接之挠奈何。家间整饬之道。果能着念。而安坐读书耶。别科有定期。汝欲观光则讲诵之事。其可忽乎。所工当在何经耶。养而方致意于易经矣。第须随所好着力也。羲经誊本旧弊者小册在于丌上。须取览也。惟当勿以一时应讲为务。宜加潜玩。以期终身受用焉。
答孙钦人(戊午)
顷书未答。即又见书甚慰。第汝妇病情。极可忧虑。日间眠食如宜否。恋恋无已。此间大都无他。而吾则一味涔涔。苦俟凉紧。而度日如年奈何。俞生所询之礼。初无可据之文。何可臆答以犯汰哉之诮哉。必欲行之则当并荐于诸位矣。至于出就厅事而行之则极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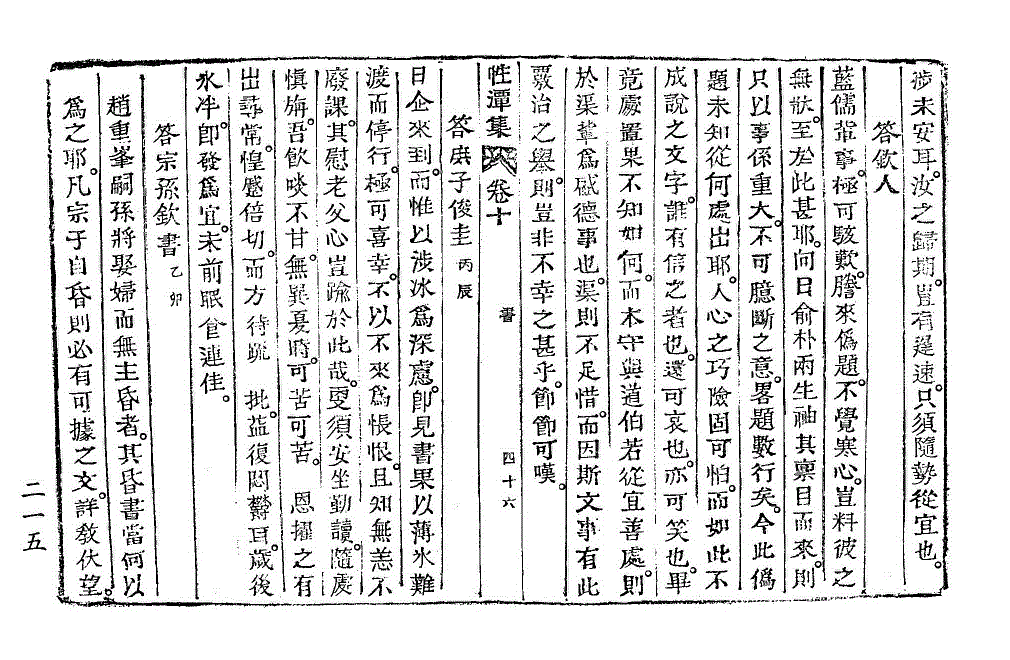 涉未安耳。汝之归期。岂有迟速。只须随势从宜也。
涉未安耳。汝之归期。岂有迟速。只须随势从宜也。答钦人
蓝儒辈事。极可骇叹。誊来伪题。不觉寒心。岂料彼之无状。至于此甚耶。向日俞朴两生袖其禀目而来。则只以事系重大。不可臆断之意。略题数行矣。今此伪题未知从何处出耶。人心之巧险固可怕。而如此不成说之文字。谁有信之者也。还可哀也。亦可笑也。毕竟处置果不知如何。而本守与道伯若从宜善处。则于渠辈为盛德事也。渠则不足惜。而因斯文事有此覈治之举。则岂非不幸之甚乎。节节可叹。
答庶子俊圭(丙辰)
日企来到。而惟以涉冰为深虑。即见书果以薄冰难渡而停行。极可喜幸。不以不来为怅恨。且知无恙不废课。其慰老父心岂踰于此哉。更须安坐勤读。随处慎旃。吾饮啖不甘。无异夏时。可苦可苦。 恩擢之有出寻常。惶蹙倍切。而方待疏 批。益复闷郁耳。岁后冰泮。即发为宜。未前眠食连佳。
答宗孙钦书(乙卯)
赵重峰嗣孙将娶妇而无主昏者。其昏书当何以为之耶。凡宗子自昏则必有可据之文。详教伏望。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6H 页
 家礼。宗子自昏则以族人之长为主。魏氏会成云孤而无族长者。母舅主之。无母舅者。父执里宰皆可。宋龟峰曰孤子冠。自称主人。而独于昏礼不称主人。为养廉远耻也。今其昏书所主称者。亦无族人之长。则恐当遵会成说。而妇人无外事则母不可为主。而其舅主之无妨。此在辑览源流二书。论之颇详。可考而知也。
家礼。宗子自昏则以族人之长为主。魏氏会成云孤而无族长者。母舅主之。无母舅者。父执里宰皆可。宋龟峰曰孤子冠。自称主人。而独于昏礼不称主人。为养廉远耻也。今其昏书所主称者。亦无族人之长。则恐当遵会成说。而妇人无外事则母不可为主。而其舅主之无妨。此在辑览源流二书。论之颇详。可考而知也。答钦书
妇人之以显辟显舅姑题主者。始于周元阳礼。而实出不得已者也。今闵真宝家之以次子旁题而权奉者。诚得矣。于其祖母丧。虽服期制。而其所题主。有何疑哉。只旁题去一孝字而已。及其三年丧毕后。改题其祖考神主。亦当如是。而待其孀嫂立后以定宗事耳。
答钦书(丙辰)
并有丧常持重服。礼家之大经也。母丧葬后则虽在父丧初期后。居常不当服齐衰矣。
妇女在家。服其兄弟之出继者。固为大功。则及其出嫁降为小功者。实不可谓之再降也。然则其兄弟之妻当为缌矣。兄弟之为父后者固不降服。而其妻则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6L 页
 当服小功耳。
当服小功耳。答钦书
尤遂两先生影帧之自松禾李氏家移奉于道东书院讲堂夹室者。诚极未安。今海西诸章甫之以移奉绍贤发议决定者。诚得稳宜。松儒之独有岐贰。殊不可知也。不然则宁可还奉于本家。而断不宜仍奉于道院矣。至于疏请之举。亦何可轻易再渎也。只当依道儒诸议而已。以是为定则遂庵真像之同奉。亦恐无所妨耳。抑有一事可商者。近闻龙津书院所奉影帧。蠹伤已甚。不可不改摹云。而此岂北儒所能办者也。远外慨悯。自不能已。若使海儒细知此事状。则惕然致念。必有以从宜变通矣。第须相议如何。
答族孙钦时(乙卯)
宗家祠堂。先世坟墓。虽在于荣归历路相望处。而不必迤入虚拜。势当到门后整衣服。诣谒告由如仪矣。荣扫时奠酌之节。固宜宗子主之。而远代则行尊者主之。至于祧位则奉祀者可以行之耳。
答钦时
祔位题主。以宗子为主。而入祔于庙。自有礼据。则今于君家事。无容更议。恐当待其立后而改题移奉矣。
性潭先生集卷之十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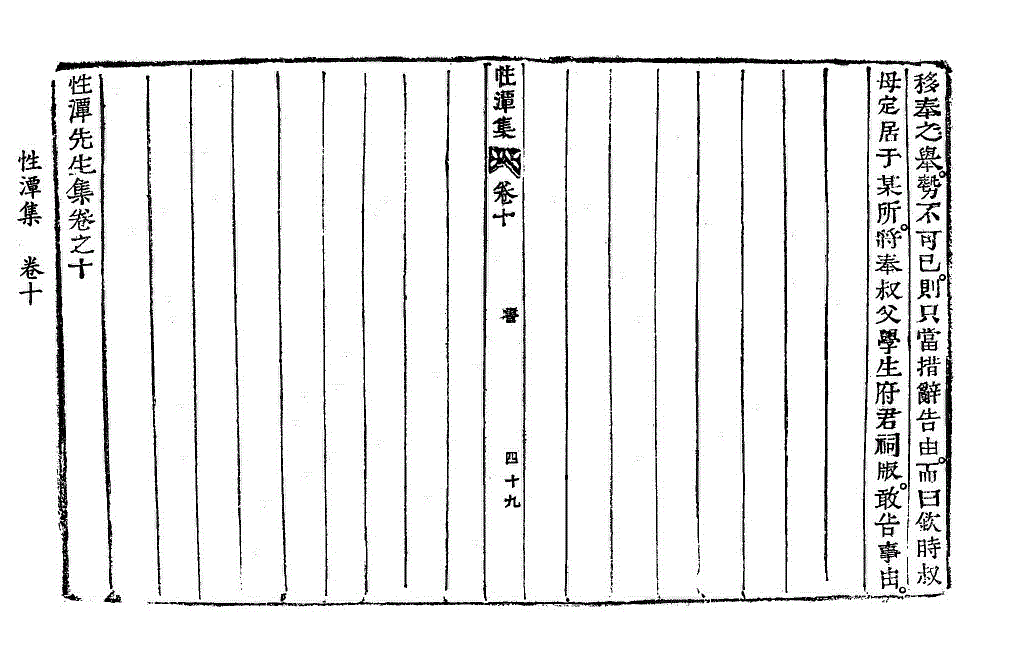 移奉之举。势不可已。则只当措辞告由。而曰钦时叔母定居于某所。将奉叔父学生府君祠版。敢告事由。
移奉之举。势不可已。则只当措辞告由。而曰钦时叔母定居于某所。将奉叔父学生府君祠版。敢告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