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耳溪集卷十九 第 x 页
耳溪集卷十九
疏劄
疏劄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38H 页
 辞弘文馆修撰书(甲戌)
辞弘文馆修撰书(甲戌)伏以臣罪在积逋。罚止薄勘。曾未几时。甄叙如旧。臣方衔恩讼愆。屏伏乡庐。即伏奉今月二十四日承政院成贴。有旨以臣为弘文馆修撰。使之乘驲上来者。臣始则惝恍。不省致此之由。终焉闷蹙。罔知措躬之所也。噫。臣本资性凡劣。最居人下。重以赋命奇薄。早失庭训。单陋寡闻。无与为比。而少不自量。随众应举。至于获窃科名。则直是侥倖偶中耳。臣于是。窃伏惟念。古人之立朝从宦者。皆必有藉手事君之资。或以经术。或以政事。其学足以需国用。其能足以应世务。然后乃敢进身而不疑也。夫如是故。外无饕荣苟禄之讥。内无丧身辱名之患。斯乃圣经所称学优则仕之律令节度也。顾臣不肖。百无一能。而惟其自知则甚审。环顾其中。实无丝粟之才可以供世者。而释褐未几。骤躐清贯。前后叨冒。罔非逾越微分者。臣非不知光宠之可怀。义分之可畏。而不敢为闻命辄膺之计者。诚以人臣事君。当以廉节为重。不亶趍走为恭也。区区愚计。窃以犬马之齿。未及强仕之限。从今以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38L 页
 往。稍能用力于古人之绪馀。赖天之灵。得免面墙之耻。不终为弃才。则出而陈力。少效尘刹之报。尚未晚矣。向一陈恳。乞得长暇者。非但为私情之闷迫而已。辞不获命。只恨忱诚之浅薄。而今又千万意外。蒙此误恩名器之玷污。自有当世之公议。臣姑不敢自列。而顾臣所以自谋其身者。转益穷隘。茫无涯畔。臣诚抚躬惭悼。无以为心也。念臣所叨职名。遴选之难。责任之重。视前尤别。苟非深于经术足资启沃之功者。莫宜居之。而臣于经典之邃奥。子史之浩穰。未尝有一日之功力。少时所受于人者。不过粗传音句。殆同儿曹之课读而已。其中盖有初未开卷者。亦有未及卒业者。夫以经训菑畬。士所当先治者。其荒疏灭裂乃如此。而况于其他乎。噫。以此不学之身。乃敢冒进于横经之列。若使猥承顾问之音。终不免矇然瞠然。左右视而不能对。则其为清朝之羞辱。听闻之传笑。当如何哉。夫事上之道。勿欺而已。使臣掩饰其不能。而贪荣冒宠。腼然自进。则固不足言矣。今也明知其不堪。而怵分畏义。嗫嚅不陈。则亦非所谓勿欺无隐之义也。其罪反不重欤。此臣所以罄泻腔血。据实陈暴。不敢恤其烦猥之诛也。倘蒙 睿度宽假曲垂。体
往。稍能用力于古人之绪馀。赖天之灵。得免面墙之耻。不终为弃才。则出而陈力。少效尘刹之报。尚未晚矣。向一陈恳。乞得长暇者。非但为私情之闷迫而已。辞不获命。只恨忱诚之浅薄。而今又千万意外。蒙此误恩名器之玷污。自有当世之公议。臣姑不敢自列。而顾臣所以自谋其身者。转益穷隘。茫无涯畔。臣诚抚躬惭悼。无以为心也。念臣所叨职名。遴选之难。责任之重。视前尤别。苟非深于经术足资启沃之功者。莫宜居之。而臣于经典之邃奥。子史之浩穰。未尝有一日之功力。少时所受于人者。不过粗传音句。殆同儿曹之课读而已。其中盖有初未开卷者。亦有未及卒业者。夫以经训菑畬。士所当先治者。其荒疏灭裂乃如此。而况于其他乎。噫。以此不学之身。乃敢冒进于横经之列。若使猥承顾问之音。终不免矇然瞠然。左右视而不能对。则其为清朝之羞辱。听闻之传笑。当如何哉。夫事上之道。勿欺而已。使臣掩饰其不能。而贪荣冒宠。腼然自进。则固不足言矣。今也明知其不堪。而怵分畏义。嗫嚅不陈。则亦非所谓勿欺无隐之义也。其罪反不重欤。此臣所以罄泻腔血。据实陈暴。不敢恤其烦猥之诛也。倘蒙 睿度宽假曲垂。体耳溪集卷十九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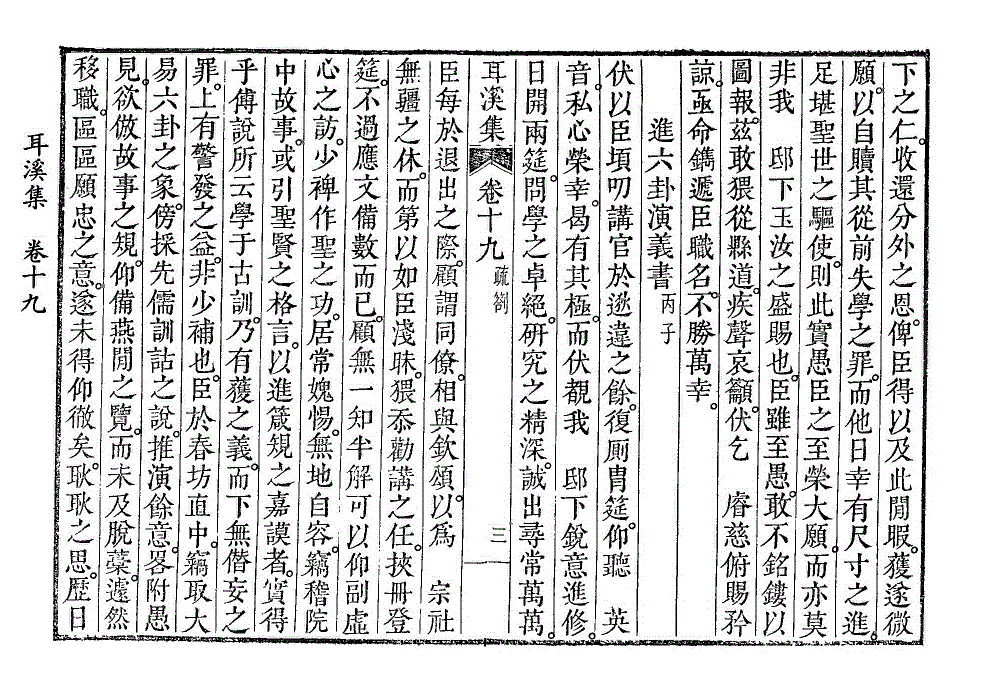 下之仁。收还分外之恩。俾臣得以及此閒暇。获遂微愿。以自赎其从前失学之罪。而他日幸有尺寸之进。足堪圣世之驱使。则此实愚臣之至荣大愿。而亦莫非我 邸下玉汝之盛赐也。臣虽至愚。敢不铭镂以图报。玆敢猥从县道。疾声哀吁。伏乞 睿慈俯赐矜谅。亟命镌递臣职名。不胜万幸。
下之仁。收还分外之恩。俾臣得以及此閒暇。获遂微愿。以自赎其从前失学之罪。而他日幸有尺寸之进。足堪圣世之驱使。则此实愚臣之至荣大愿。而亦莫非我 邸下玉汝之盛赐也。臣虽至愚。敢不铭镂以图报。玆敢猥从县道。疾声哀吁。伏乞 睿慈俯赐矜谅。亟命镌递臣职名。不胜万幸。进六卦演义书(丙子)
伏以臣顷叨讲官于逖违之馀。复厕胄筵。仰听 英音。私心荣幸。曷有其极。而伏睹我 邸下锐意进修。日开两筵。问学之卓绝。研究之精深。诚出寻常万万。臣每于退出之际。顾谓同僚。相与钦颂。以为 宗社无疆之休。而第以如臣浅昧。猥忝劝讲之任。挟册登筵。不过应文备数而已。顾无一知半解可以仰副虚心之访。少裨作圣之功。居常愧惕。无地自容。窃稽院中故事。或引圣贤之格言。以进箴规之嘉谟者。实得乎傅说所云学于古训。乃有获之义。而下无僭妄之罪。上有警发之益。非少补也。臣于春坊直中。窃取大易六卦之象。傍采先儒训诂之说。推演馀意。略附愚见。欲仿故事之规。仰备燕閒之览。而未及脱藁。遽然移职。区区愿忠之意。遂未得仰彻矣。耿耿之思。历日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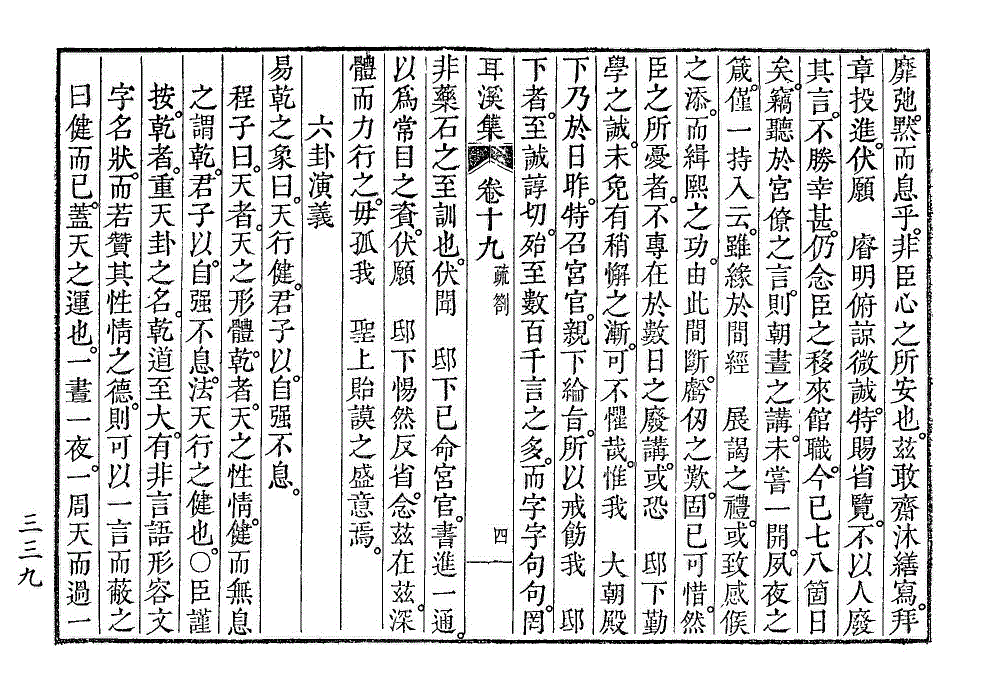 靡弛。默而息乎。非臣心之所安也。玆敢斋沐缮写。拜章投进。伏愿 睿明俯谅微诚。特赐省览。不以人废其言。不胜幸甚。仍念臣之移来馆职。今已七八个日矣。窃听于宫僚之言。则朝昼之讲。未尝一开。夙夜之箴。仅一持入云。虽缘于间经 展谒之礼。或致感候之添。而缉熙之功。由此间断。亏仞之叹。固已可惜。然臣之所忧者。不专在于数日之废讲。或恐 邸下勤学之诚。未免有稍懈之渐。可不惧哉。惟我 大朝殿下乃于日昨。特召宫官。亲下纶旨。所以戒饬我 邸下者。至诚谆切。殆至数百千言之多。而字字句句。罔非药石之至训也。伏闻 邸下已命宫官。书进一通。以为常目之资。伏愿 邸下惕然反省。念玆在玆。深体而力行之。毋孤我 圣上贻谟之盛意焉。
靡弛。默而息乎。非臣心之所安也。玆敢斋沐缮写。拜章投进。伏愿 睿明俯谅微诚。特赐省览。不以人废其言。不胜幸甚。仍念臣之移来馆职。今已七八个日矣。窃听于宫僚之言。则朝昼之讲。未尝一开。夙夜之箴。仅一持入云。虽缘于间经 展谒之礼。或致感候之添。而缉熙之功。由此间断。亏仞之叹。固已可惜。然臣之所忧者。不专在于数日之废讲。或恐 邸下勤学之诚。未免有稍懈之渐。可不惧哉。惟我 大朝殿下乃于日昨。特召宫官。亲下纶旨。所以戒饬我 邸下者。至诚谆切。殆至数百千言之多。而字字句句。罔非药石之至训也。伏闻 邸下已命宫官。书进一通。以为常目之资。伏愿 邸下惕然反省。念玆在玆。深体而力行之。毋孤我 圣上贻谟之盛意焉。六卦演义
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程子曰。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谓乾。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臣谨按。乾者。重天卦之名。乾道至大。有非言语形容文字名状。而若赞其性情之德。则可以一言而蔽之曰健而已。盖天之运也。一昼一夜。一周天而过一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0H 页
 度。以里计之。则一日之间。凡行九十馀万里。以人验之。则一息之间。已行八十馀里。不如是则无以育万物而成岁功。故曰。天行健。圣人之与天合德者。亦惟曰法其健而已。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言天之健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言文王之健也。故子思子赞之曰。纯亦不已。文王圣人也。至诚无息。固已与天无间。而若夫学圣希天之功。必先乎自强。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者。奋励勤笃之谓也。不息者。无间断作辍之谓也。而自强。又不息之工夫也。方今三阳回泰。万化维新。在 邸下法天对时之工。亦维自强而已。伏愿 邸下自强于学。而无一刻之怠忽。如天之成岁功也。自强于政。而无一事之废旷。如天之育万物也。随时随事。念玆在玆。则文王之纯亦不已。庶不专美于前矣。惟 邸下懋哉。
度。以里计之。则一日之间。凡行九十馀万里。以人验之。则一息之间。已行八十馀里。不如是则无以育万物而成岁功。故曰。天行健。圣人之与天合德者。亦惟曰法其健而已。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言天之健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言文王之健也。故子思子赞之曰。纯亦不已。文王圣人也。至诚无息。固已与天无间。而若夫学圣希天之功。必先乎自强。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者。奋励勤笃之谓也。不息者。无间断作辍之谓也。而自强。又不息之工夫也。方今三阳回泰。万化维新。在 邸下法天对时之工。亦维自强而已。伏愿 邸下自强于学。而无一刻之怠忽。如天之成岁功也。自强于政。而无一事之废旷。如天之育万物也。随时随事。念玆在玆。则文王之纯亦不已。庶不专美于前矣。惟 邸下懋哉。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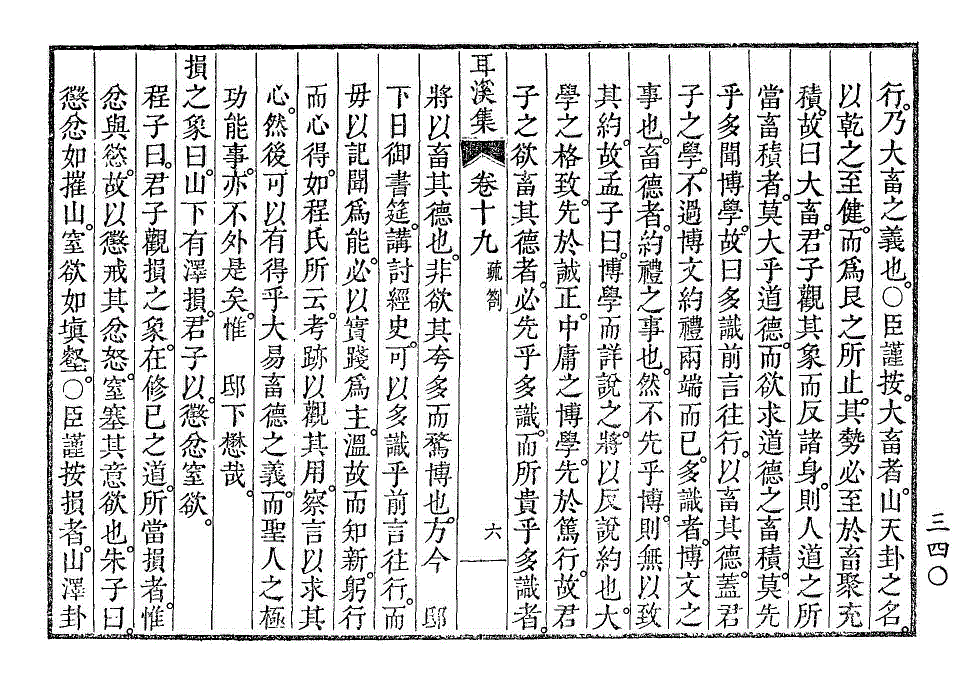 行。乃大畜之义也。○臣谨按。大畜者。山天卦之名。以乾之至健。而为艮之所止。其势必至于畜聚充积。故曰大畜。君子观其象而反诸身。则人道之所当畜积者。莫大乎道德。而欲求道德之畜积。莫先乎多闻博学。故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盖君子之学。不过博文约礼两端而已。多识者。博文之事也。畜德者。约礼之事也。然不先乎博。则无以致其约。故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大学之格致。先于诚正。中庸之博学。先于笃行。故君子之欲畜其德者。必先乎多识。而所贵乎多识者。将以畜其德也。非欲其夸多而骛博也。方今 邸下日御书筵。讲讨经史。可以多识乎前言往行。而毋以记闻为能。必以实践为主。温故而知新。躬行而心得。如程氏所云。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然后可以有得乎大易畜德之义。而圣人之极功能事。亦不外是矣。惟邸下懋哉。
行。乃大畜之义也。○臣谨按。大畜者。山天卦之名。以乾之至健。而为艮之所止。其势必至于畜聚充积。故曰大畜。君子观其象而反诸身。则人道之所当畜积者。莫大乎道德。而欲求道德之畜积。莫先乎多闻博学。故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盖君子之学。不过博文约礼两端而已。多识者。博文之事也。畜德者。约礼之事也。然不先乎博。则无以致其约。故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大学之格致。先于诚正。中庸之博学。先于笃行。故君子之欲畜其德者。必先乎多识。而所贵乎多识者。将以畜其德也。非欲其夸多而骛博也。方今 邸下日御书筵。讲讨经史。可以多识乎前言往行。而毋以记闻为能。必以实践为主。温故而知新。躬行而心得。如程氏所云。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然后可以有得乎大易畜德之义。而圣人之极功能事。亦不外是矣。惟邸下懋哉。损之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程子曰。君子观损之象。在修己之道。所当损者。惟忿与欲。故以惩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朱子曰。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臣谨按损者。山泽卦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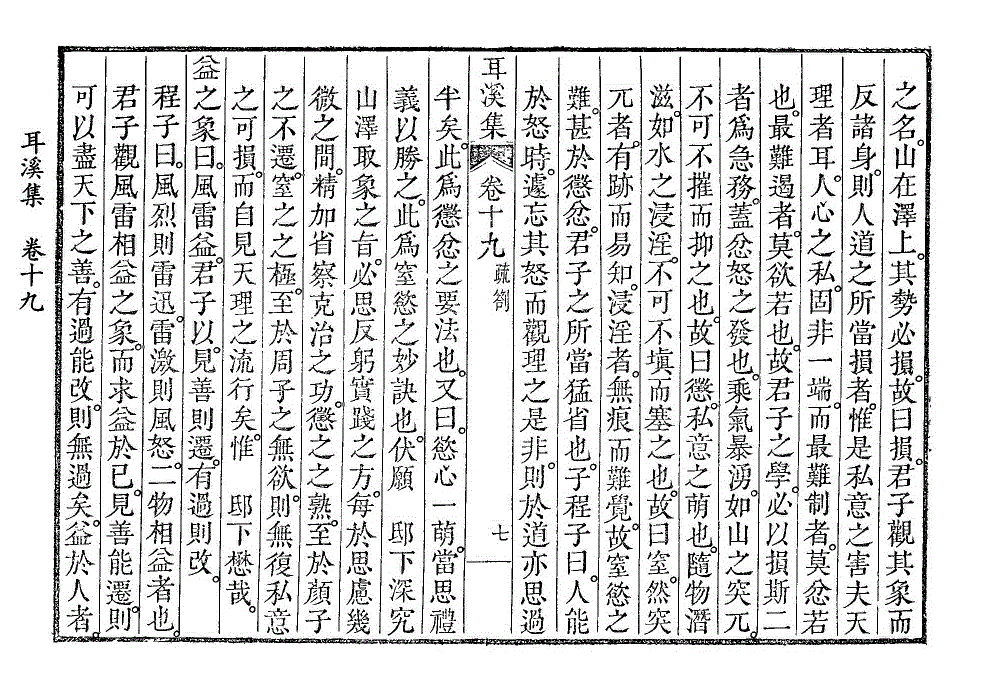 之名。山在泽上。其势必损。故曰损。君子观其象而反诸身。则人道之所当损者。惟是私意之害夫天理者耳。人心之私。固非一端。而最难制者。莫忿若也。最难遏者。莫欲若也。故君子之学。必以损斯二者为急务。盖忿怒之发也。乘气暴涌。如山之突兀。不可不摧而抑之也。故曰惩。私意之萌也。随物潜滋。如水之浸淫。不可不填而塞之也。故曰窒。然突兀者。有迹而易知。浸淫者。无痕而难觉。故窒欲之难。甚于惩忿。君子之所当猛省也。子程子曰。人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则于道亦思过半矣。此为惩忿之要法也。又曰。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此为窒欲之妙诀也。伏愿 邸下深究山泽取象之旨。必思反躬实践之方。每于思虑几微之间。精加省察克治之功。惩之之熟。至于颜子之不迁。窒之之极。至于周子之无欲。则无复私意之可损。而自见天理之流行矣。惟 邸下懋哉。
之名。山在泽上。其势必损。故曰损。君子观其象而反诸身。则人道之所当损者。惟是私意之害夫天理者耳。人心之私。固非一端。而最难制者。莫忿若也。最难遏者。莫欲若也。故君子之学。必以损斯二者为急务。盖忿怒之发也。乘气暴涌。如山之突兀。不可不摧而抑之也。故曰惩。私意之萌也。随物潜滋。如水之浸淫。不可不填而塞之也。故曰窒。然突兀者。有迹而易知。浸淫者。无痕而难觉。故窒欲之难。甚于惩忿。君子之所当猛省也。子程子曰。人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则于道亦思过半矣。此为惩忿之要法也。又曰。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此为窒欲之妙诀也。伏愿 邸下深究山泽取象之旨。必思反躬实践之方。每于思虑几微之间。精加省察克治之功。惩之之熟。至于颜子之不迁。窒之之极。至于周子之无欲。则无复私意之可损。而自见天理之流行矣。惟 邸下懋哉。益之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程子曰。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观风雷相益之象。而求益于己。见善能迁。则可以尽天下之善。有过能改。则无过矣。益于人者。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1L 页
 无大于是。朱子曰。迁善当如风之速。改过当如雷之猛。○臣谨按。益者。风雷卦之名。程朱之说备矣。然人情孰不欲求益。而迁善之不勇。改过之或吝者。何哉。志不立而私意间之也。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善而内自省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又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乃立志祛私之方也。诚愿我 邸下见一善焉。必自省曰。我能有是耶。苟不能焉。则必发愤而跂及之。不能不措也。见一不善。必自省曰。我亦有是耶。苟有是焉。则必用力而克治之。不祛不措也。铢积而寸累。日就而月将。则终至于万善俱足而无过可改矣。岂不休哉。惟 邸下懋哉。
无大于是。朱子曰。迁善当如风之速。改过当如雷之猛。○臣谨按。益者。风雷卦之名。程朱之说备矣。然人情孰不欲求益。而迁善之不勇。改过之或吝者。何哉。志不立而私意间之也。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善而内自省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又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乃立志祛私之方也。诚愿我 邸下见一善焉。必自省曰。我能有是耶。苟不能焉。则必发愤而跂及之。不能不措也。见一不善。必自省曰。我亦有是耶。苟有是焉。则必用力而克治之。不祛不措也。铢积而寸累。日就而月将。则终至于万善俱足而无过可改矣。岂不休哉。惟 邸下懋哉。颐之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程子曰。卦义上止而下动。卦体外实而中虚。为颐口之象。口所以养人也。故君子观其象。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则必当而无失。在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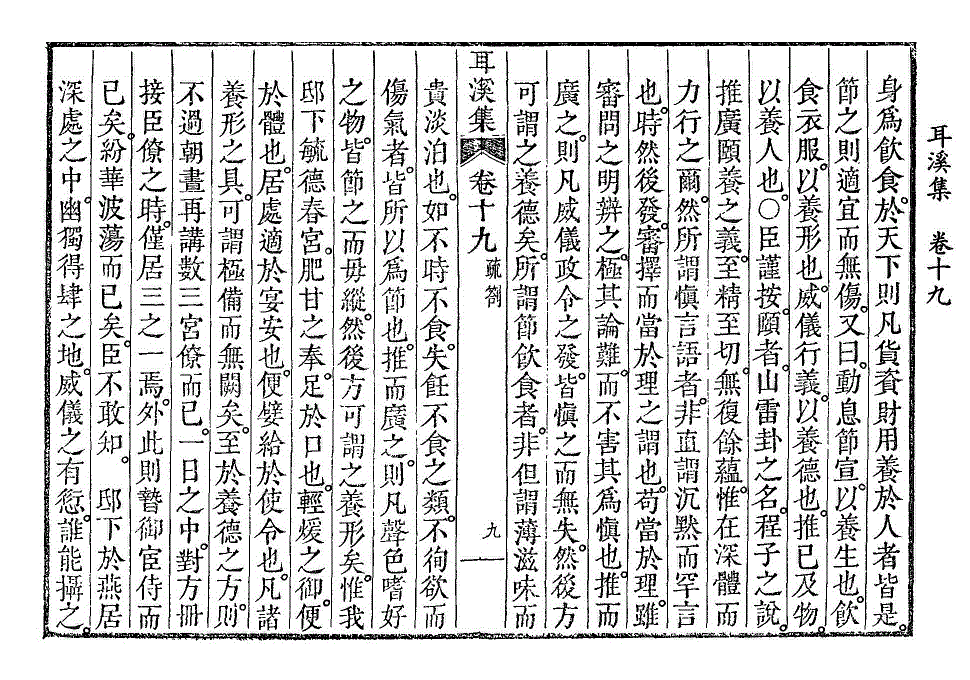 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养于人者皆是。节之则适宜而无伤。又曰。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臣谨按。颐者。山雷卦之名。程子之说。推广颐养之义。至精至切。无复馀蕴。惟在深体而力行之尔。然所谓慎言语者。非直谓沉默而罕言也。时然后发。审择而当于理之谓也。苟当于理。虽审问之。明辨之。极其论难。而不害其为慎也。推而广之。则凡威仪政令之发。皆慎之而无失。然后方可谓之养德矣。所谓节饮食者。非但谓薄滋味而贵淡泊也。如不时不食。失饪不食之类。不徇欲而伤气者。皆所以为节也。推而广之。则凡声色嗜好之物。皆节之而毋纵。然后方可谓之养形矣。惟我邸下毓德春宫。肥甘之奉。足于口也。轻煖之御。便于体也。居处适于宴安也。便嬖给于使令也。凡诸养形之具。可谓极备而无阙矣。至于养德之方。则不过朝昼再讲数三宫僚而已。一日之中。对方册接臣僚之时。仅居三之一焉。外此则亵御宦侍而已矣。纷华波荡而已矣。臣不敢知。 邸下于燕居深处之中。幽独得肆之地。威仪之有愆。谁能摄之。
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养于人者皆是。节之则适宜而无伤。又曰。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臣谨按。颐者。山雷卦之名。程子之说。推广颐养之义。至精至切。无复馀蕴。惟在深体而力行之尔。然所谓慎言语者。非直谓沉默而罕言也。时然后发。审择而当于理之谓也。苟当于理。虽审问之。明辨之。极其论难。而不害其为慎也。推而广之。则凡威仪政令之发。皆慎之而无失。然后方可谓之养德矣。所谓节饮食者。非但谓薄滋味而贵淡泊也。如不时不食。失饪不食之类。不徇欲而伤气者。皆所以为节也。推而广之。则凡声色嗜好之物。皆节之而毋纵。然后方可谓之养形矣。惟我邸下毓德春宫。肥甘之奉。足于口也。轻煖之御。便于体也。居处适于宴安也。便嬖给于使令也。凡诸养形之具。可谓极备而无阙矣。至于养德之方。则不过朝昼再讲数三宫僚而已。一日之中。对方册接臣僚之时。仅居三之一焉。外此则亵御宦侍而已矣。纷华波荡而已矣。臣不敢知。 邸下于燕居深处之中。幽独得肆之地。威仪之有愆。谁能摄之。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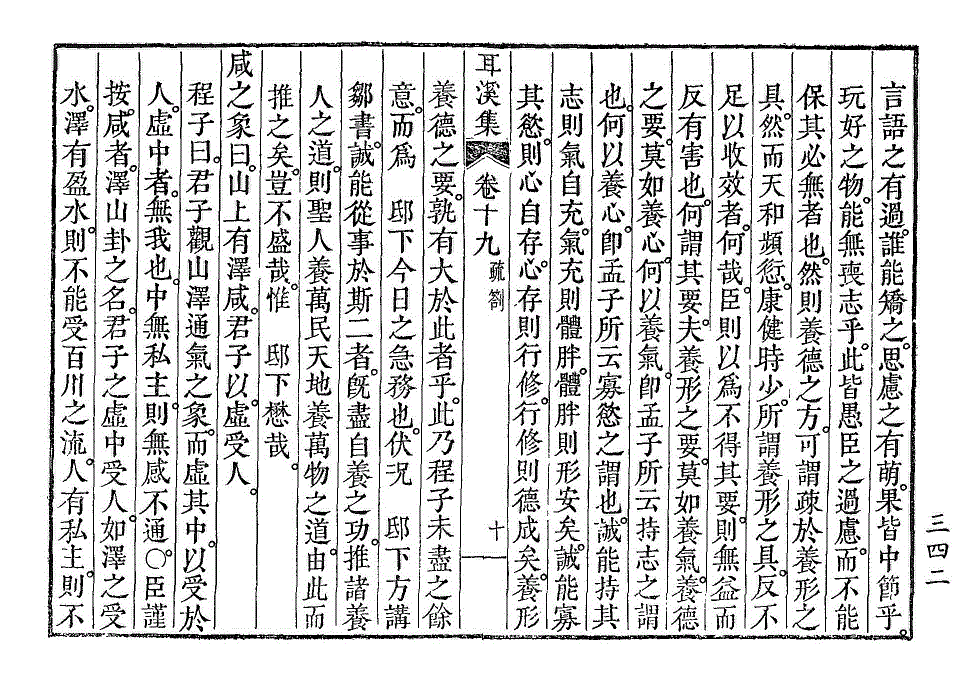 言语之有过。谁能矫之。思虑之有萌。果皆中节乎。玩好之物。能无丧志乎。此皆愚臣之过虑。而不能保其必无者也。然则养德之方。可谓疏于养形之具。然而天和频愆。康健时少。所谓养形之具。反不足以收效者。何哉。臣则以为不得其要。则无益而反有害也。何谓其要。夫养形之要。莫如养气。养德之要。莫如养心。何以养气。即孟子所云持志之谓也。何以养心。即孟子所云寡欲之谓也。诚能持其志则气自充。气充则体胖。体胖则形安矣。诚能寡其欲。则心自存。心存则行修。行修则德成矣。养形养德之要。孰有大于此者乎。此乃程子未尽之馀意。而为 邸下今日之急务也。伏况 邸下方讲邹书。诚能从事于斯二者。既尽自养之功。推诸养人之道。则圣人养万民天地养万物之道。由此而推之矣。岂不盛哉。惟邸下懋哉。
言语之有过。谁能矫之。思虑之有萌。果皆中节乎。玩好之物。能无丧志乎。此皆愚臣之过虑。而不能保其必无者也。然则养德之方。可谓疏于养形之具。然而天和频愆。康健时少。所谓养形之具。反不足以收效者。何哉。臣则以为不得其要。则无益而反有害也。何谓其要。夫养形之要。莫如养气。养德之要。莫如养心。何以养气。即孟子所云持志之谓也。何以养心。即孟子所云寡欲之谓也。诚能持其志则气自充。气充则体胖。体胖则形安矣。诚能寡其欲。则心自存。心存则行修。行修则德成矣。养形养德之要。孰有大于此者乎。此乃程子未尽之馀意。而为 邸下今日之急务也。伏况 邸下方讲邹书。诚能从事于斯二者。既尽自养之功。推诸养人之道。则圣人养万民天地养万物之道。由此而推之矣。岂不盛哉。惟邸下懋哉。咸之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程子曰。君子观山泽通气之象。而虚其中。以受于人。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臣谨按。咸者。泽山卦之名。君子之虚中受人。如泽之受水。泽有盈水。则不能受百川之流。人有私主。则不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3H 页
 能来天下之善。所谓无私主者。不主一己之私见。必尽天下之公理也。故为学而不能虚中。则无以资切磋之益。居上而不能虚中。则无以闻忠谏之言。虽以颜子之学。亦曰。有若无实若虚矣。以舜禹之圣。亦尝舍己从人。拜昌曰俞矣。大哉。虚受之义也。惟我 邸下睿学虽已夙就。德义虽已无阙。勿生自满之志。克体无我之道。讲学必尽虚心之访。临下思闻逆耳之言。毋以先入为主。毋以偏听为明。则学虽就而益进。德无阙而愈修矣。伊尹之训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仲虺之告汤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惟邸下懋哉。
能来天下之善。所谓无私主者。不主一己之私见。必尽天下之公理也。故为学而不能虚中。则无以资切磋之益。居上而不能虚中。则无以闻忠谏之言。虽以颜子之学。亦曰。有若无实若虚矣。以舜禹之圣。亦尝舍己从人。拜昌曰俞矣。大哉。虚受之义也。惟我 邸下睿学虽已夙就。德义虽已无阙。勿生自满之志。克体无我之道。讲学必尽虚心之访。临下思闻逆耳之言。毋以先入为主。毋以偏听为明。则学虽就而益进。德无阙而愈修矣。伊尹之训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仲虺之告汤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惟邸下懋哉。右六卦之象。即孔子所系之辞。而卦体之下。必称君子以者。使人即物穷理而反求诸身也。六十四卦之象。何莫非至理所寓。而就其最切于圣学者。莫如此六者。故臣于两筵讲读之暇。积费䌷绎檃括之功。拈出经文。立为纲领。次述程朱之说。以发本经之旨。继又窃附愚见。仰备 睿览僭妄之罪。实无所逃。然皆推演经传之馀意。无一言一句。刱出无稽之说者也。盖此六象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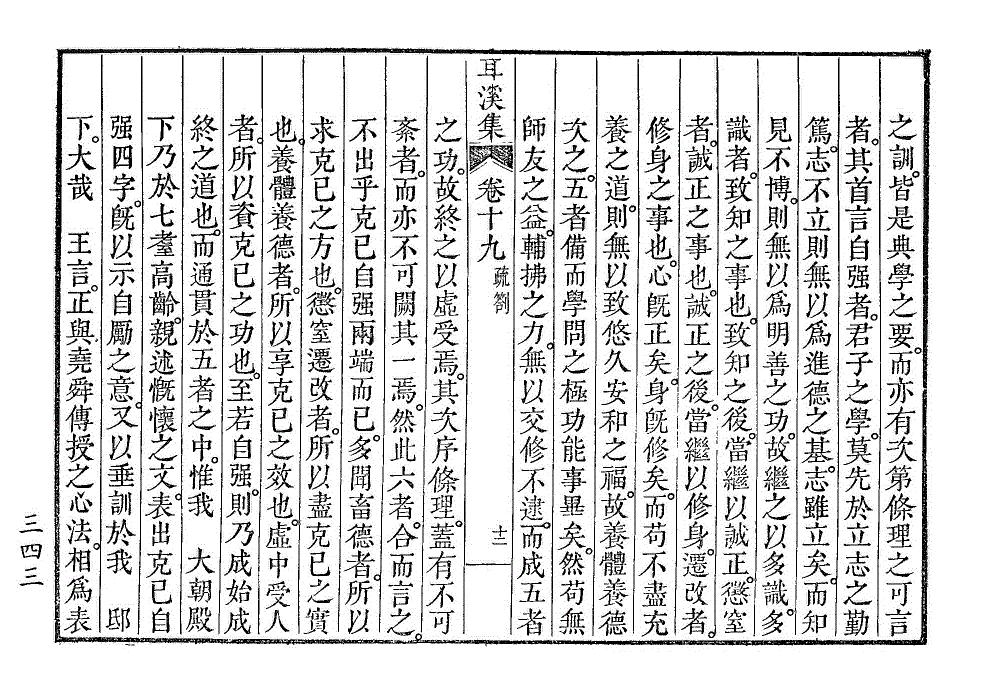 之训。皆是典学之要。而亦有次第条理之可言者。其首言自强者。君子之学。莫先于立志之勤笃。志不立则无以为进德之基。志虽立矣。而知见不博。则无以为明善之功。故继之以多识。多识者。致知之事也。致知之后。当继以诚正。惩窒者。诚正之事也。诚正之后。当继以修身。迁改者。修身之事也。心既正矣。身既修矣。而苟不尽充养之道。则无以致悠久安和之福。故养体养德次之。五者备而学问之极功能事毕矣。然苟无师友之益。辅拂之力。无以交修不逮。而成五者之功。故终之以虚受焉。其次序条理。盖有不可紊者。而亦不可阙其一焉。然此六者。合而言之。不出乎克己自强两端而已。多闻畜德者。所以求克己之方也。惩窒迁改者。所以尽克己之实也。养体养德者。所以享克己之效也。虚中受人者。所以资克己之功也。至若自强。则乃成始成终之道也。而通贯于五者之中。惟我 大朝殿下乃于七耋高龄。亲述慨怀之文。表出克己自强四字。既以示自励之意。又以垂训于我 邸下。大哉 王言。正与尧舜传授之心法。相为表
之训。皆是典学之要。而亦有次第条理之可言者。其首言自强者。君子之学。莫先于立志之勤笃。志不立则无以为进德之基。志虽立矣。而知见不博。则无以为明善之功。故继之以多识。多识者。致知之事也。致知之后。当继以诚正。惩窒者。诚正之事也。诚正之后。当继以修身。迁改者。修身之事也。心既正矣。身既修矣。而苟不尽充养之道。则无以致悠久安和之福。故养体养德次之。五者备而学问之极功能事毕矣。然苟无师友之益。辅拂之力。无以交修不逮。而成五者之功。故终之以虚受焉。其次序条理。盖有不可紊者。而亦不可阙其一焉。然此六者。合而言之。不出乎克己自强两端而已。多闻畜德者。所以求克己之方也。惩窒迁改者。所以尽克己之实也。养体养德者。所以享克己之效也。虚中受人者。所以资克己之功也。至若自强。则乃成始成终之道也。而通贯于五者之中。惟我 大朝殿下乃于七耋高龄。亲述慨怀之文。表出克己自强四字。既以示自励之意。又以垂训于我 邸下。大哉 王言。正与尧舜传授之心法。相为表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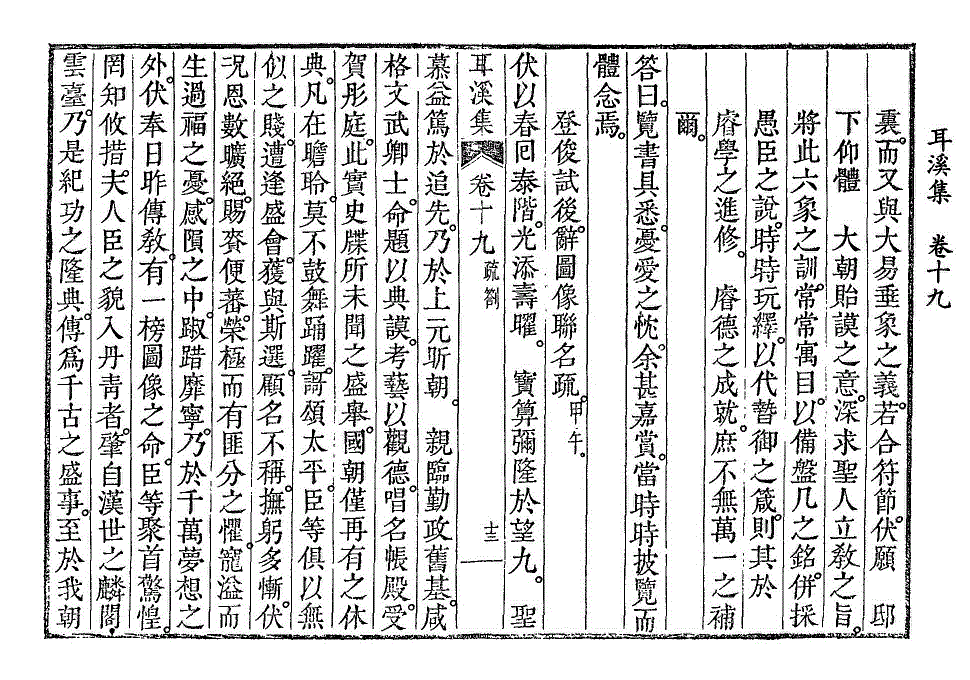 里。而又与大易垂象之义。若合符节。伏愿 邸下仰体 大朝贻谟之意。深求圣人立教之旨。将此六象之训。常常寓目。以备盘几之铭。并采愚臣之说。时时玩绎。以代亵御之箴。则其于 睿学之进修。 睿德之成就。庶不无万一之补尔。
里。而又与大易垂象之义。若合符节。伏愿 邸下仰体 大朝贻谟之意。深求圣人立教之旨。将此六象之训。常常寓目。以备盘几之铭。并采愚臣之说。时时玩绎。以代亵御之箴。则其于 睿学之进修。 睿德之成就。庶不无万一之补尔。答曰。览书具悉。忧爱之忱。余甚嘉赏。当时时披览而体念焉。
登俊试后。辞图像联名疏。(甲午)
伏以春回泰阶。光添寿曜。 宝算弥隆于望九。 圣慕益笃于追先。乃于上元昕朝。 亲临勤政旧基。咸格文武卿士。命题以典谟。考艺以观德。唱名帐殿。受贺彤庭。此实史牒所未闻之盛举。国朝仅再有之休典。凡在瞻聆。莫不鼓舞踊跃。歌颂太平。臣等俱以无似之贱。遭逢盛会。获与斯选。顾名不称。抚躬多惭。伏况恩数旷绝。赐赉便蕃。荣极而有匪分之惧。宠溢而生过福之忧。感陨之中。踧踖靡宁。乃于千万梦想之外。伏奉日昨传教。有一榜图像之命。臣等聚首惊惶。罔知攸措。夫人臣之貌入丹青者。肇自汉世之麟阁,云台。乃是纪功之隆典。传为千古之盛事。至于我朝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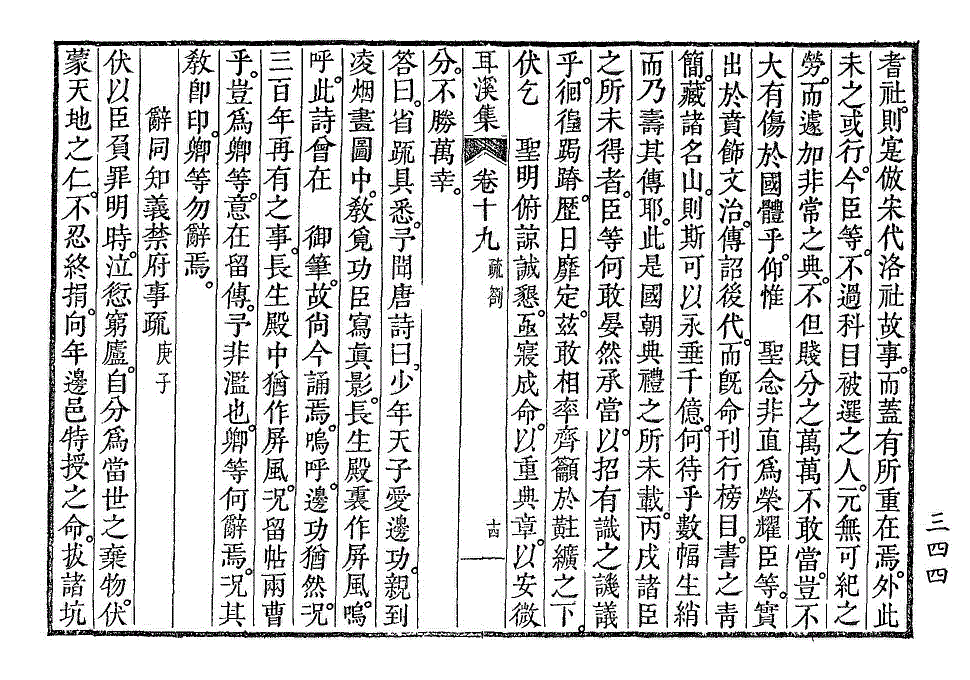 耆社。则寔仿宋代洛社故事。而盖有所重在焉。外此未之或行。今臣等。不过科目被选之人。元无可纪之劳。而遽加非常之典。不但贱分之万万不敢当。岂不大有伤于国体乎。仰惟 圣念非直为荣耀臣等。实出于贲饰文治。传诏后代。而既命刊行榜目。书之青简。藏诸名山。则斯可以永垂千亿。何待乎数幅生绡而乃寿其传耶。此是国朝典礼之所未载。丙戌诸臣之所未得者。臣等何敢晏然承当。以招有识之讥议乎。徊徨跼蹐。历日靡定。玆敢相率齐吁于黈纩之下伏乞 圣明俯谅诚恳。亟寝成命。以重典章。以安微分。不胜万幸。
耆社。则寔仿宋代洛社故事。而盖有所重在焉。外此未之或行。今臣等。不过科目被选之人。元无可纪之劳。而遽加非常之典。不但贱分之万万不敢当。岂不大有伤于国体乎。仰惟 圣念非直为荣耀臣等。实出于贲饰文治。传诏后代。而既命刊行榜目。书之青简。藏诸名山。则斯可以永垂千亿。何待乎数幅生绡而乃寿其传耶。此是国朝典礼之所未载。丙戌诸臣之所未得者。臣等何敢晏然承当。以招有识之讥议乎。徊徨跼蹐。历日靡定。玆敢相率齐吁于黈纩之下伏乞 圣明俯谅诚恳。亟寝成命。以重典章。以安微分。不胜万幸。答曰。省疏具悉。予闻唐诗曰。少年天子爱边功。亲到凌烟画图中。教觅功臣写真影。长生殿里作屏风。呜呼。此诗曾在 御笔。故尚今诵焉。呜呼。边功犹然。况三百年再有之事。长生殿中犹作屏风。况留帖两曹乎。岂为卿等。意在留传。予非滥也。卿等何辞焉。况其教即印。卿等勿辞焉。
辞同知义禁府事疏(庚子)
伏以臣负罪明时。泣愆穷庐。自分为当世之弃物。伏蒙天地之仁。不忍终捐。向年边邑特授之命。拔诸坑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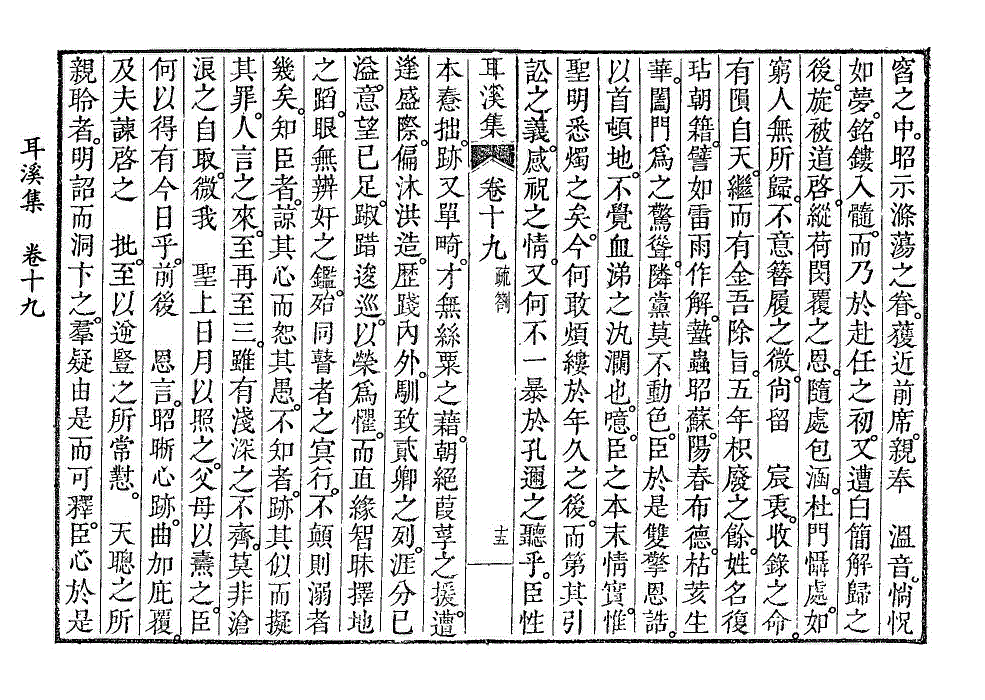 窞之中。昭示涤荡之眷。获近前席。亲奉 温音。惝恍如梦。铭镂入髓。而乃于赴任之初。又遭白简解归之后。旋被道启。纵荷闵覆之恩。随处包涵。杜门慑处。如穷人无所归。不意簪履之微。尚留 宸衷。收录之命。有陨自天。继而有金吾除旨。五年枳废之馀。姓名复玷朝籍。譬如雷雨作解。蛰虫昭苏。阳春布德。枯荄生华。阖门为之惊耸。邻党莫不动色。臣于是双擎恩诰。以首顿地。不觉血涕之汍澜也。噫。臣之本末情实。惟圣明悉烛之矣。今何敢烦缕于年久之后。而第其引讼之义。感祝之情。又何不一暴于孔迩之听乎。臣性本憃拙。迹又单畸。才无丝粟之藉。朝绝葭莩之援。遭逢盛际。偏沐洪造。历践内外。驯致贰卿之列。涯分已溢。意望已足。踧踖逡巡。以荣为惧。而直缘智昧择地之蹈。眼无辨奸之鉴。殆同瞽者之冥行。不颠则溺者几矣。知臣者。谅其心而恕其愚。不知者。迹其似而拟其罪。人言之来。至再至三。虽有浅深之不齐。莫非沧浪之自取。微我 圣上日月以照之。父母以焘之。臣何以得有今日乎。前后 恩言。昭晰心迹。曲加庇覆。及夫谏启之 批。至以逆竖之所常怼。 天聪之所亲聆者。明诏而洞卞之。群疑由是而可释。臣心于是
窞之中。昭示涤荡之眷。获近前席。亲奉 温音。惝恍如梦。铭镂入髓。而乃于赴任之初。又遭白简解归之后。旋被道启。纵荷闵覆之恩。随处包涵。杜门慑处。如穷人无所归。不意簪履之微。尚留 宸衷。收录之命。有陨自天。继而有金吾除旨。五年枳废之馀。姓名复玷朝籍。譬如雷雨作解。蛰虫昭苏。阳春布德。枯荄生华。阖门为之惊耸。邻党莫不动色。臣于是双擎恩诰。以首顿地。不觉血涕之汍澜也。噫。臣之本末情实。惟圣明悉烛之矣。今何敢烦缕于年久之后。而第其引讼之义。感祝之情。又何不一暴于孔迩之听乎。臣性本憃拙。迹又单畸。才无丝粟之藉。朝绝葭莩之援。遭逢盛际。偏沐洪造。历践内外。驯致贰卿之列。涯分已溢。意望已足。踧踖逡巡。以荣为惧。而直缘智昧择地之蹈。眼无辨奸之鉴。殆同瞽者之冥行。不颠则溺者几矣。知臣者。谅其心而恕其愚。不知者。迹其似而拟其罪。人言之来。至再至三。虽有浅深之不齐。莫非沧浪之自取。微我 圣上日月以照之。父母以焘之。臣何以得有今日乎。前后 恩言。昭晰心迹。曲加庇覆。及夫谏启之 批。至以逆竖之所常怼。 天聪之所亲聆者。明诏而洞卞之。群疑由是而可释。臣心于是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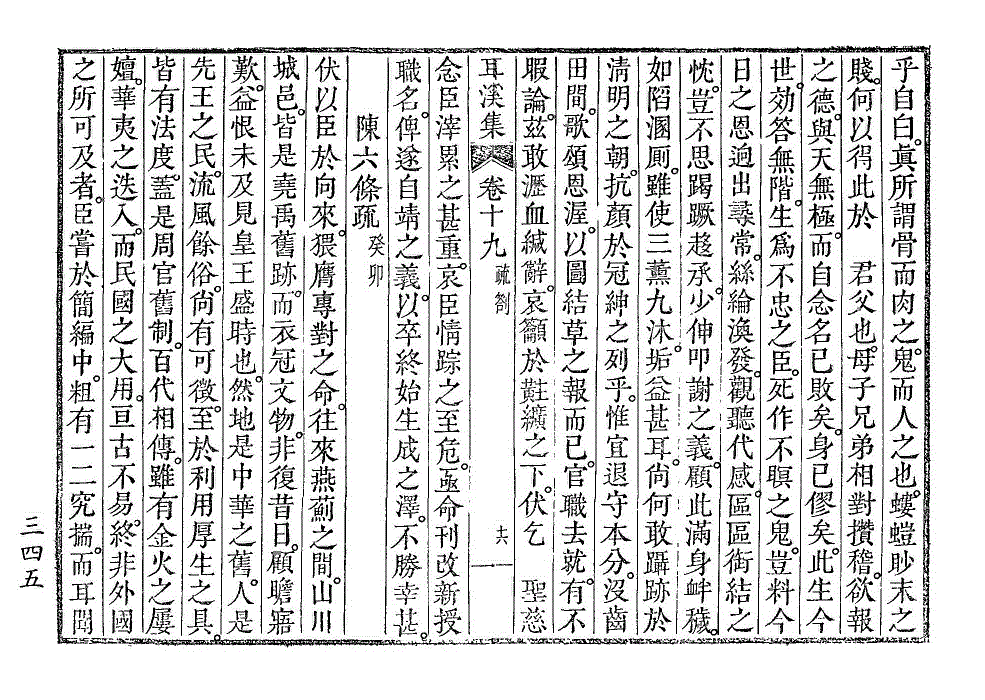 乎自白。真所谓骨而肉之。鬼而人之也。蝼蚁眇末之贱。何以得此于 君父也。母子兄弟相对攒稽。欲报之德。与天无极。而自念名已败矣。身已僇矣。此生今世。效答无阶。生为不忠之臣。死作不瞑之鬼。岂料今日之恩迥出寻常。丝纶涣发。观听代感。区区衔结之忱。岂不思𨃃蹶趍承。少伸叩谢之义。顾此满身衅秽。如陷溷厕。虽使三薰九沐。垢益甚耳。尚何敢蹑迹于清明之朝。抗颜于冠绅之列乎。惟宜退守本分。没齿田间。歌颂恩渥。以图结草之报而已。官职去就。有不暇论。玆敢沥血缄辞。哀吁于黈纩之下。伏乞 圣慈念臣滓累之甚重。哀臣情踪之至危。亟命刊改新授职名。俾遂自靖之义。以卒终始生成之泽。不胜幸甚。
乎自白。真所谓骨而肉之。鬼而人之也。蝼蚁眇末之贱。何以得此于 君父也。母子兄弟相对攒稽。欲报之德。与天无极。而自念名已败矣。身已僇矣。此生今世。效答无阶。生为不忠之臣。死作不瞑之鬼。岂料今日之恩迥出寻常。丝纶涣发。观听代感。区区衔结之忱。岂不思𨃃蹶趍承。少伸叩谢之义。顾此满身衅秽。如陷溷厕。虽使三薰九沐。垢益甚耳。尚何敢蹑迹于清明之朝。抗颜于冠绅之列乎。惟宜退守本分。没齿田间。歌颂恩渥。以图结草之报而已。官职去就。有不暇论。玆敢沥血缄辞。哀吁于黈纩之下。伏乞 圣慈念臣滓累之甚重。哀臣情踪之至危。亟命刊改新授职名。俾遂自靖之义。以卒终始生成之泽。不胜幸甚。陈六条疏(癸卯)
伏以臣于向来。猥膺专对之命。往来燕蓟之间。山川城邑。皆是尧禹旧迹。而衣冠文物。非复昔日。顾瞻寤叹。益恨未及见皇王盛时也。然地是中华之旧。人是先王之民。流风馀俗。尚有可徵。至于利用厚生之具。皆有法度。盖是周官旧制。百代相传。虽有金火之屡嬗。华夷之迭入。而民国之大用。亘古不易。终非外国之所可及者。臣尝于简编中。粗有一二究揣。而耳闻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6H 页
 不如目见。乃今身履其地。益有犁然可信者。夫观风询俗。使臣职也。凡厥出疆之臣。率多采闻见。陈别单之例。臣谨取其有裨于国计。最切于民用者。分为六条。开列于左。惟 圣明垂察焉。
不如目见。乃今身履其地。益有犁然可信者。夫观风询俗。使臣职也。凡厥出疆之臣。率多采闻见。陈别单之例。臣谨取其有裨于国计。最切于民用者。分为六条。开列于左。惟 圣明垂察焉。一曰车制。昔黄帝氏始作舟车。以济不通。又有作干戈。造律吕。测历象等事。孰非圣人刱物之智。而黄帝之号。必加轩辕者。可见万世之功。莫盛于造车也。古者言国之大小。必称车乘。土地之广。财赋之盛。孰非人君之富。而独数车之众寡。斯有千乘万乘之号焉。可见有国之用。莫大于车也。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各一其官。而独于车也。有轮人舆人车人辀人等职。径围尺寸之制。长短崇博之式。纤悉如画。足令人手按而斤斲焉。先儒言曰。车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法易之三才六画。又可见生民之器莫重于车也。夫如是。故行则有乘车焉。战则有戎车焉。任载有大车。农家有役车。灌田有水车。千百其制。各致其用。内而中国。外而四裔。莫不用车。传所称舟车所至。霜露所坠者。可见通天下无有不用车之地也。试以今行所见言之。燕京之内。轮毂相击。填街溢巷。苟非贱隶窭儿。则举皆乘车而行。自燕至辽千馀里之间。轨辙相连。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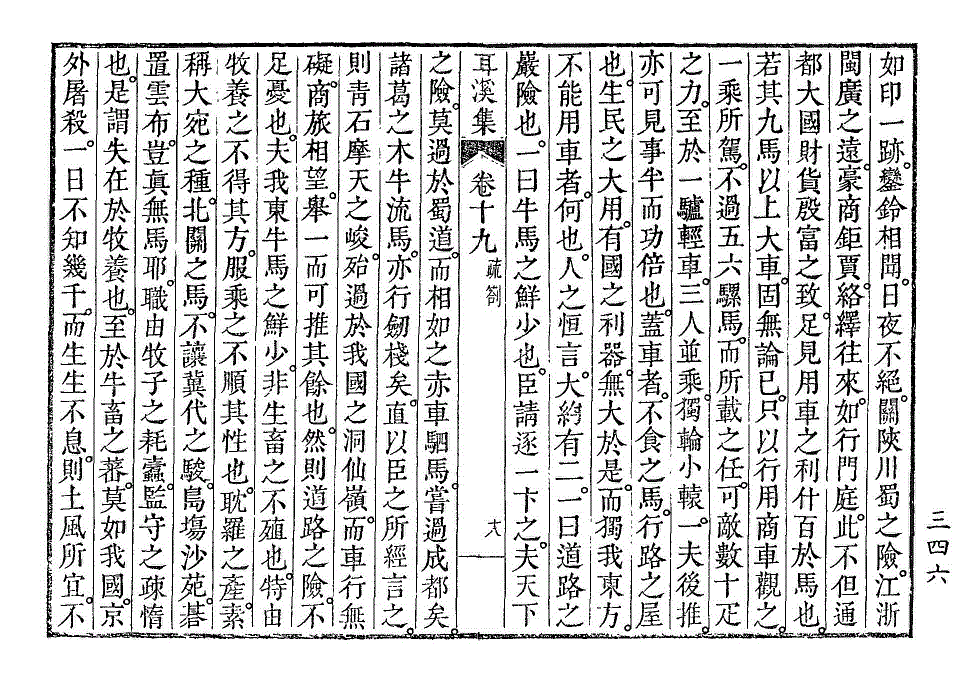 如印一迹。銮铃相闻。日夜不绝。关陜川蜀之险。江浙闽广之远。豪商钜贾。络绎往来。如行门庭。此不但通都大国财货殷富之致。足见用车之利什百于马也。若其九马以上大车。固无论已。只以行用商车观之。一乘所驾。不过五六骡马。而所载之任。可敌数十疋之力。至于一驴轻车。三人并乘。独轮小辕。一夫后推。亦可见事半而功倍也。盖车者。不食之马。行路之屋也。生民之大用。有国之利器。无大于是。而独我东方。不能用车者。何也。人之恒言。大约有二。一曰道路之岩险也。一曰牛马之鲜少也。臣请逐一卞之。夫天下之险。莫过于蜀道。而相如之赤车驷马。尝过成都矣。诸葛之木牛流马。亦行剑栈矣。直以臣之所经言之。则青石摩天之峻。殆过于我国之洞仙岭。而车行无碍。商旅相望。举一而可推其馀也。然则道路之险。不足忧也。夫我东牛马之鲜少。非生畜之不殖也。特由牧养之不得其方。服乘之不顺其性也。耽罗之产。素称大宛之种。北关之马。不让冀代之骏。岛场沙苑。棋置云布。岂真无马耶。职由牧子之耗蠹。监守之疏惰也。是谓失在于牧养也。至于牛畜之蕃。莫如我国。京外屠杀。一日不知几千。而生生不息。则土风所宜。不
如印一迹。銮铃相闻。日夜不绝。关陜川蜀之险。江浙闽广之远。豪商钜贾。络绎往来。如行门庭。此不但通都大国财货殷富之致。足见用车之利什百于马也。若其九马以上大车。固无论已。只以行用商车观之。一乘所驾。不过五六骡马。而所载之任。可敌数十疋之力。至于一驴轻车。三人并乘。独轮小辕。一夫后推。亦可见事半而功倍也。盖车者。不食之马。行路之屋也。生民之大用。有国之利器。无大于是。而独我东方。不能用车者。何也。人之恒言。大约有二。一曰道路之岩险也。一曰牛马之鲜少也。臣请逐一卞之。夫天下之险。莫过于蜀道。而相如之赤车驷马。尝过成都矣。诸葛之木牛流马。亦行剑栈矣。直以臣之所经言之。则青石摩天之峻。殆过于我国之洞仙岭。而车行无碍。商旅相望。举一而可推其馀也。然则道路之险。不足忧也。夫我东牛马之鲜少。非生畜之不殖也。特由牧养之不得其方。服乘之不顺其性也。耽罗之产。素称大宛之种。北关之马。不让冀代之骏。岛场沙苑。棋置云布。岂真无马耶。职由牧子之耗蠹。监守之疏惰也。是谓失在于牧养也。至于牛畜之蕃。莫如我国。京外屠杀。一日不知几千。而生生不息。则土风所宜。不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7H 页
 言可知。经曰。服牛乘马。盖谓牛宜于服箱。马宜于骑乘。未尝言用马载物也。传曰。牛以引重。马以致远。引重者。引车之称。非谓以背负重也。致远者。行远之称。非谓致物于远也。于以见马宜骑行。而引重之力。不如牛。牛可服箱。而致远之健。不如马也。亦未尝言用牛载物也。我国则不然。牛马皆任其背。牛则尚可。马其殆矣。由是之故。江上载米之马。率半年而一易。城中运柴之蹄。过三冬而力尽。大抵不毙则躄牵。以之屠肆矣。此岂马之罪哉。是谓失在于服乘也。然则二者之说穷矣。何苦而不用车也。臣则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非不为也。盖未尝求行之之术也。岂惟是哉。君子安于循常。不欲为通变之论。众人忸于见闻。不乐为稀异之事。故国家未尝设法而禁之。终无一人刱行者。虽或有慨然有志者。而苟非朝廷之令。则力有所不及。行之有不便焉耳。臣尝宦游诸路。亦见国中多用车之处。岭南之安东,义城。海西之长渊,信川。关北之咸兴以南六镇诸邑。皆用一两牛之车。运谷载柴。往来数百里之间。而制样粗钝。不能行远。专由于未得其法。而亦可见车无不可行之理也。今欲行车。莫如取法于中国。先令诸军门及两西监兵营。义
言可知。经曰。服牛乘马。盖谓牛宜于服箱。马宜于骑乘。未尝言用马载物也。传曰。牛以引重。马以致远。引重者。引车之称。非谓以背负重也。致远者。行远之称。非谓致物于远也。于以见马宜骑行。而引重之力。不如牛。牛可服箱。而致远之健。不如马也。亦未尝言用牛载物也。我国则不然。牛马皆任其背。牛则尚可。马其殆矣。由是之故。江上载米之马。率半年而一易。城中运柴之蹄。过三冬而力尽。大抵不毙则躄牵。以之屠肆矣。此岂马之罪哉。是谓失在于服乘也。然则二者之说穷矣。何苦而不用车也。臣则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非不为也。盖未尝求行之之术也。岂惟是哉。君子安于循常。不欲为通变之论。众人忸于见闻。不乐为稀异之事。故国家未尝设法而禁之。终无一人刱行者。虽或有慨然有志者。而苟非朝廷之令。则力有所不及。行之有不便焉耳。臣尝宦游诸路。亦见国中多用车之处。岭南之安东,义城。海西之长渊,信川。关北之咸兴以南六镇诸邑。皆用一两牛之车。运谷载柴。往来数百里之间。而制样粗钝。不能行远。专由于未得其法。而亦可见车无不可行之理也。今欲行车。莫如取法于中国。先令诸军门及两西监兵营。义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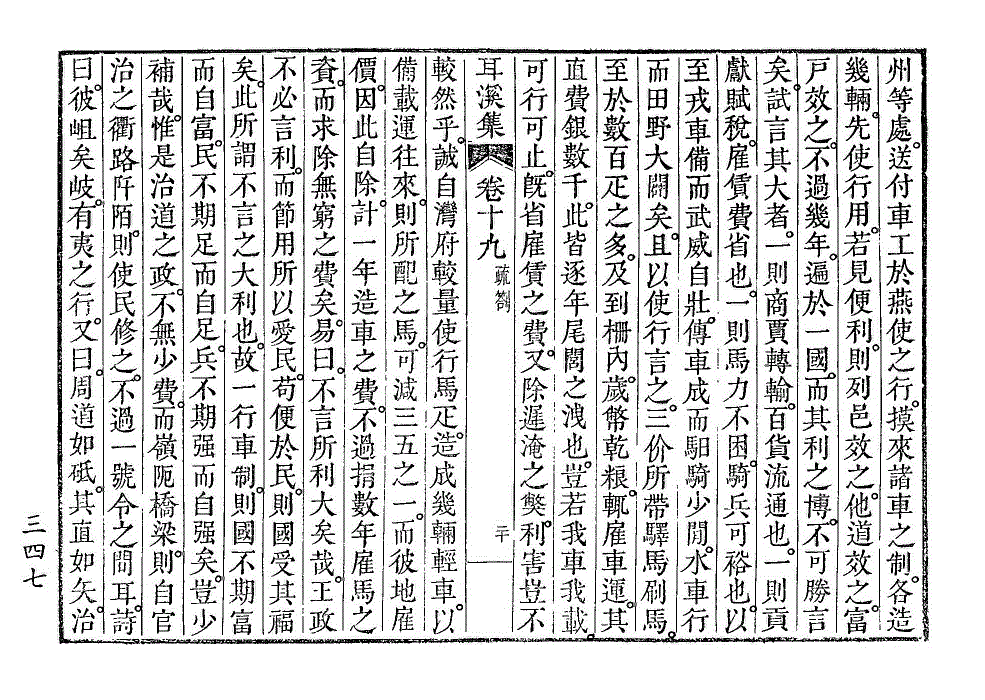 州等处。送付车工于燕使之行。摸来诸车之制。各造几辆。先使行用。若见便利。则列邑效之。他道效之。富户效之。不过几年。遍于一国。而其利之博。不可胜言矣。试言其大者。一则商贾转输。百货流通也。一则贡献赋税。雇赁费省也。一则马力不困。骑兵可裕也。以至戎车备而武威自壮。传车成而驲骑少閒。水车行而田野大辟矣。且以使行言之。三价所带驿马刷马。至于数百疋之多。及到栅内。岁币乾粮。辄雇车运。其直费银数千。此皆逐年尾闾之泄也。岂若我车我载。可行可止。既省雇赁之费。又除迟淹之弊。利害岂不较然乎。诚自湾府较量使行马疋。造成几辆轻车。以备载运往来。则所配之马。可减三五之一。而彼地雇价。因此自除。计一年造车之费。不过捐数年雇马之资。而求除无穷之费矣。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王政不必言利。而节用所以爱民。苟便于民。则国受其福矣。此所谓不言之大利也。故一行车制。则国不期富而自富。民不期足而自足。兵不期强而自强矣。岂少补哉。惟是治道之政。不无少费。而岭阨桥梁。则自官治之衢路阡陌。则使民修之。不过一号令之间耳。诗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
州等处。送付车工于燕使之行。摸来诸车之制。各造几辆。先使行用。若见便利。则列邑效之。他道效之。富户效之。不过几年。遍于一国。而其利之博。不可胜言矣。试言其大者。一则商贾转输。百货流通也。一则贡献赋税。雇赁费省也。一则马力不困。骑兵可裕也。以至戎车备而武威自壮。传车成而驲骑少閒。水车行而田野大辟矣。且以使行言之。三价所带驿马刷马。至于数百疋之多。及到栅内。岁币乾粮。辄雇车运。其直费银数千。此皆逐年尾闾之泄也。岂若我车我载。可行可止。既省雇赁之费。又除迟淹之弊。利害岂不较然乎。诚自湾府较量使行马疋。造成几辆轻车。以备载运往来。则所配之马。可减三五之一。而彼地雇价。因此自除。计一年造车之费。不过捐数年雇马之资。而求除无穷之费矣。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王政不必言利。而节用所以爱民。苟便于民。则国受其福矣。此所谓不言之大利也。故一行车制。则国不期富而自富。民不期足而自足。兵不期强而自强矣。岂少补哉。惟是治道之政。不无少费。而岭阨桥梁。则自官治之衢路阡陌。则使民修之。不过一号令之间耳。诗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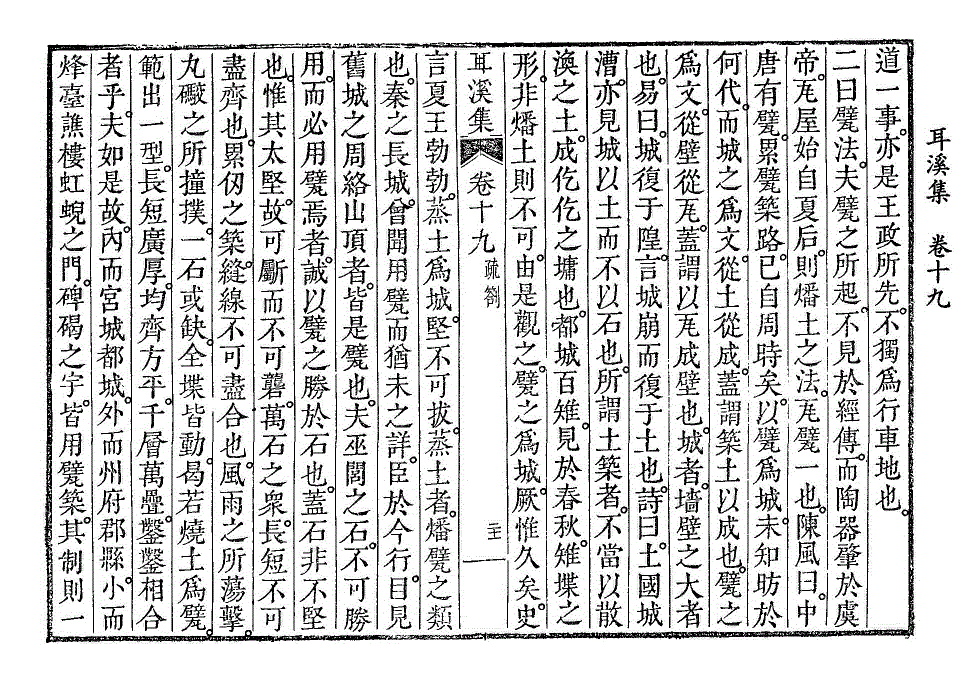 道一事。亦是王政所先。不独为行车地也。
道一事。亦是王政所先。不独为行车地也。二曰甓法。夫甓之所起。不见于经传。而陶器肇于虞帝。瓦屋始自夏后。则燔土之法。瓦甓一也。陈风曰。中唐有甓。累甓筑路。已自周时矣。以甓为城。未知昉于何代。而城之为文。从土从成。盖谓筑土以成也。甓之为文。从壁从瓦。盖谓以瓦成壁也。城者。墙壁之大者也。易曰。城复于隍。言城崩而复于土也。诗曰。土国城漕。亦见城以土而不以石也。所谓土筑者。不当以散涣之土。成仡仡之墉也。都城百雉。见于春秋。雉堞之形。非燔土则不可。由是观之。甓之为城。厥惟久矣。史言夏王勃勃。蒸土为城。坚不可拔。蒸土者。燔甓之类也。秦之长城。曾闻用甓而犹未之详。臣于今行。目见旧城之周络山顶者。皆是甓也。夫巫闾之石。不可胜用。而必用甓焉者。诚以甓之胜于石也。盖石非不坚也。惟其太坚。故可斸而不可砻。万石之众。长短不可尽齐也。累仞之筑。缝线不可尽合也。风雨之所荡击。九炮之所撞扑。一石或缺。全堞皆动。曷若烧土为甓。范出一型。长短广厚。均齐方平。千层万叠。凿凿相合者乎。夫如是故。内而宫城都城。外而州府郡县。小而烽台谯楼虹蜺之门。碑碣之宇。皆用甓筑。其制则一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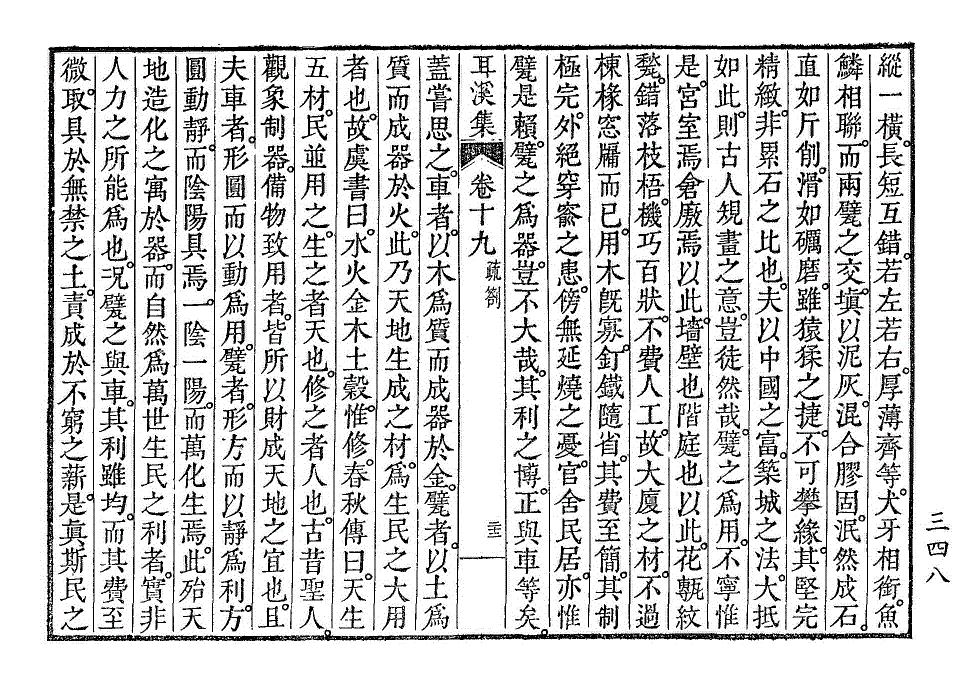 纵一横。长短互错。若左若右。厚薄齐等。犬牙相衔。鱼鳞相联。而两甓之交。填以泥灰。混合胶固。泯然成石。直如斤削。滑如砺磨。虽猿猱之捷。不可攀缘。其坚完精致。非累石之比也。夫以中国之富。筑城之法。大抵如此。则古人规画之意。岂徒然哉。甓之为用。不宁惟是。宫室焉仓廒焉以此。墙壁也阶庭也以此。花砖纹甃。错落枝梧。机巧百状。不费人工。故大厦之材。不过栋椽窗牖而已。用木既寡。钉铁随省。其费至简。其制极完。外绝穿窬之患。傍无延烧之忧。官舍民居。亦惟甓是赖。甓之为器。岂不大哉。其利之博。正与车等矣。盖尝思之。车者。以木为质而成器于金。甓者。以土为质而成器于火。此乃天地生成之材。为生民之大用者也。故虞书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春秋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生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古昔圣人。观象制器。备物致用者。皆所以财成天地之宜也。且夫车者。形圆而以动为用。甓者。形方而以静为利。方圆动静。而阴阳具焉。一阴一阳。而万化生焉。此殆天地造化之寓于器。而自然为万世生民之利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况甓之与车。其利虽均。而其费至微。取具于无禁之土。责成于不穷之薪。是真斯民之
纵一横。长短互错。若左若右。厚薄齐等。犬牙相衔。鱼鳞相联。而两甓之交。填以泥灰。混合胶固。泯然成石。直如斤削。滑如砺磨。虽猿猱之捷。不可攀缘。其坚完精致。非累石之比也。夫以中国之富。筑城之法。大抵如此。则古人规画之意。岂徒然哉。甓之为用。不宁惟是。宫室焉仓廒焉以此。墙壁也阶庭也以此。花砖纹甃。错落枝梧。机巧百状。不费人工。故大厦之材。不过栋椽窗牖而已。用木既寡。钉铁随省。其费至简。其制极完。外绝穿窬之患。傍无延烧之忧。官舍民居。亦惟甓是赖。甓之为器。岂不大哉。其利之博。正与车等矣。盖尝思之。车者。以木为质而成器于金。甓者。以土为质而成器于火。此乃天地生成之材。为生民之大用者也。故虞书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春秋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生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古昔圣人。观象制器。备物致用者。皆所以财成天地之宜也。且夫车者。形圆而以动为用。甓者。形方而以静为利。方圆动静。而阴阳具焉。一阴一阳。而万化生焉。此殆天地造化之寓于器。而自然为万世生民之利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况甓之与车。其利虽均。而其费至微。取具于无禁之土。责成于不穷之薪。是真斯民之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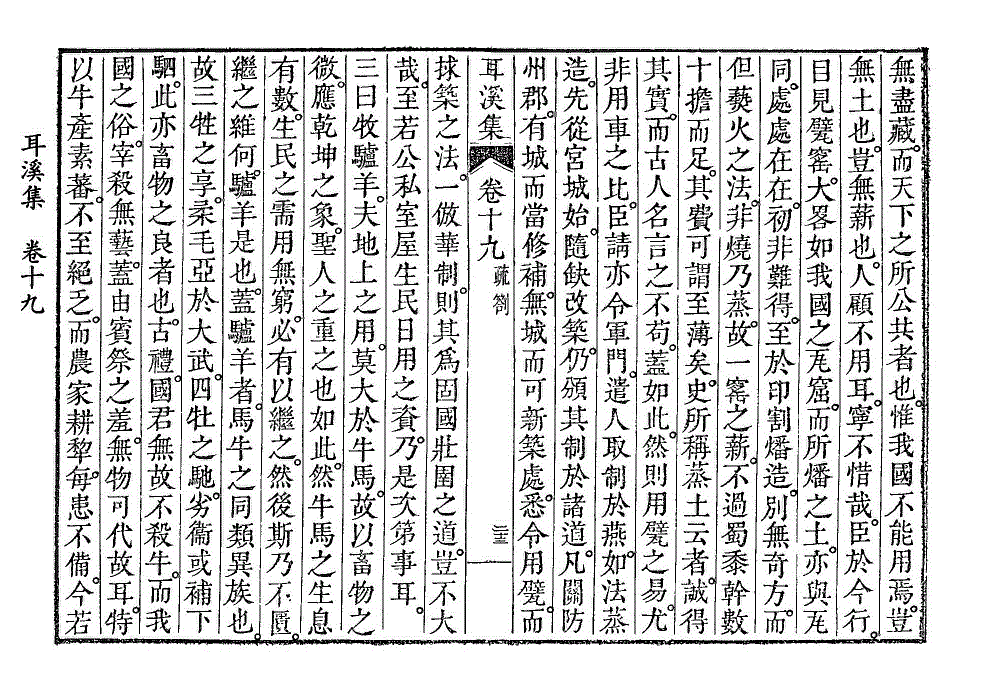 无尽藏。而天下之所公共者也。惟我国不能用焉。岂无土也。岂无薪也。人顾不用耳。宁不惜哉。臣于今行。目见甓窑。大略如我国之瓦窟。而所燔之土。亦与瓦同。处处在在。初非难得。至于印割燔造。别无奇方。而但爇火之法。非烧乃蒸。故一窑之薪。不过蜀黍干数十担而足。其费可谓至薄矣。史所称蒸土云者。诚得其实。而古人名言之不苟。盖如此。然则用甓之易。尤非用车之比。臣请亦令军门。遣人取制于燕。如法蒸造。先从宫城始。随缺改筑。仍颁其制于诸道。凡关防州郡。有城而当修补。无城而可新筑处。悉令用甓。而救筑之法。一仿华制。则其为固国壮圉之道。岂不大哉。至若公私室屋生民日用之资。乃是次第事耳。
无尽藏。而天下之所公共者也。惟我国不能用焉。岂无土也。岂无薪也。人顾不用耳。宁不惜哉。臣于今行。目见甓窑。大略如我国之瓦窟。而所燔之土。亦与瓦同。处处在在。初非难得。至于印割燔造。别无奇方。而但爇火之法。非烧乃蒸。故一窑之薪。不过蜀黍干数十担而足。其费可谓至薄矣。史所称蒸土云者。诚得其实。而古人名言之不苟。盖如此。然则用甓之易。尤非用车之比。臣请亦令军门。遣人取制于燕。如法蒸造。先从宫城始。随缺改筑。仍颁其制于诸道。凡关防州郡。有城而当修补。无城而可新筑处。悉令用甓。而救筑之法。一仿华制。则其为固国壮圉之道。岂不大哉。至若公私室屋生民日用之资。乃是次第事耳。三曰牧驴羊。夫地上之用。莫大于牛马。故以畜物之微。应乾坤之象。圣人之重之也如此。然牛马之生息有数。生民之需用无穷。必有以继之。然后斯乃不匮。继之维何。驴羊是也。盖驴羊者。马牛之同类异族也。故三牲之享。柔毛亚于大武。四牡之驰。劣卫或补下驷。此亦畜物之良者也。古礼。国君无故不杀牛。而我国之俗。宰杀无艺。盖由宾祭之羞。无物可代故耳。特以牛产素蕃。不至绝乏。而农家耕犁。每患不备。今若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49L 页
 多畜羊羔。以代俎实。则牛不过耗。而耕有馀耦矣。况羊之为物。最称易生。列于六畜。遍于四方。皮毛肠角。靡不中用。故臣于出疆之前。已有陈白。今行略有贸来。而每年历贡之行。边门之市。辄令和买。渐致孳息。则可以救万牛之命。开三农之利矣。驴之为物。健不如马。而性驯易使。价轻易求。故中国之人。家家畜之。以之驾车。以之载物。以之服犁。或令磨粟运水。惟意指使。如僮仆然。其代人劳而分马力甚大。至若骡者。出于驴而健于驴。真同雀生鹯而貙生狼也。任重致远。实兼牛马之长。故明皇幸蜀。尝乘青骡而疾驰。宋之姚平仲。乘白骡。一日踔八百里。信蹄物之奇品也。况又其性易长。堕地半年。辄胜骑驰。故华人之爱之也。有甚于马。我国驴骡。虽有自北来者。未尝孳长。力尽而毙。是不娴畜牧之过也。诚能多贸燕市。放诸牧场。取其种息。以备国用。则服乘有馀。戎马自足。而车制若行。则用以驾载。可当牛马之半。商旅流行。民蒙其利矣。大抵。畜牧之政。费小而利远。畜驴羊。乃所以蕃牛马也。牛马蕃。则民富而兵强矣。
多畜羊羔。以代俎实。则牛不过耗。而耕有馀耦矣。况羊之为物。最称易生。列于六畜。遍于四方。皮毛肠角。靡不中用。故臣于出疆之前。已有陈白。今行略有贸来。而每年历贡之行。边门之市。辄令和买。渐致孳息。则可以救万牛之命。开三农之利矣。驴之为物。健不如马。而性驯易使。价轻易求。故中国之人。家家畜之。以之驾车。以之载物。以之服犁。或令磨粟运水。惟意指使。如僮仆然。其代人劳而分马力甚大。至若骡者。出于驴而健于驴。真同雀生鹯而貙生狼也。任重致远。实兼牛马之长。故明皇幸蜀。尝乘青骡而疾驰。宋之姚平仲。乘白骡。一日踔八百里。信蹄物之奇品也。况又其性易长。堕地半年。辄胜骑驰。故华人之爱之也。有甚于马。我国驴骡。虽有自北来者。未尝孳长。力尽而毙。是不娴畜牧之过也。诚能多贸燕市。放诸牧场。取其种息。以备国用。则服乘有馀。戎马自足。而车制若行。则用以驾载。可当牛马之半。商旅流行。民蒙其利矣。大抵。畜牧之政。费小而利远。畜驴羊。乃所以蕃牛马也。牛马蕃。则民富而兵强矣。四曰禁铜器。臣闻天地之生物也。各专其性。圣人之理财也。各适其职。相侵则两病。偏重则有缺。此不易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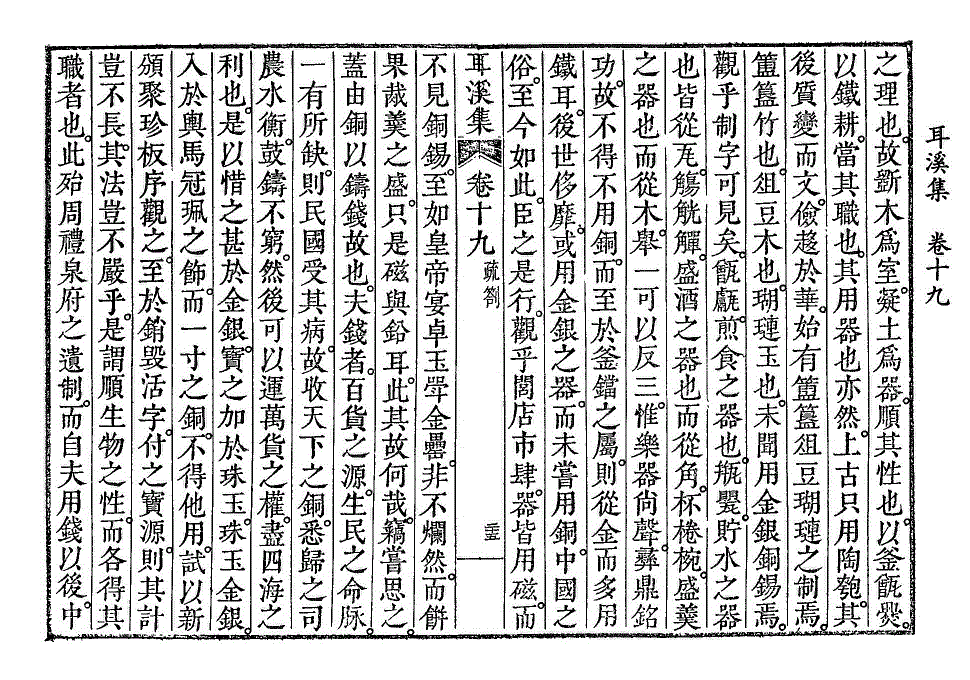 之理也。故斲木为室。凝土为器。顺其性也。以釜甑爨。以铁耕。当其职也。其用器也亦然。上古只用陶匏。其后质变而文。俭趍于华。始有簠簋俎豆瑚琏之制焉。簠簋竹也。俎豆木也。瑚琏玉也。未闻用金银铜锡焉。观乎制字可见矣。甑甗。煎食之器也。瓶罂。贮水之器也皆从瓦。觞觥觯。盛酒之器也而从角。杯棬碗。盛羹之器也而从木。举一可以反三。惟乐器尚声。彝鼎铭功。故不得不用铜。而至于釜铛之属。则从金而多用铁耳。后世侈靡。或用金银之器。而未尝用铜。中国之俗。至今如此。臣之是行。观乎闾店市肆。器皆用磁。而不见铜锡。至如皇帝宴卓玉斝金罍。非不烂然。而饼果胾羹之盛。只是磁与铅耳。此其故何哉。窃尝思之。盖由铜以铸钱故也。夫钱者。百货之源。生民之命脉。一有所缺。则民国受其病。故收天下之铜。悉归之司农水衡。鼓铸不穷。然后可以运万货之权。尽四海之利也。是以惜之甚于金银。宝之加于珠玉。珠玉金银。入于舆马冠佩之饰。而一寸之铜。不得他用。试以新颁聚珍板序观之。至于销毁活字。付之宝源。则其计岂不长。其法岂不严乎。是谓顺生物之性。而各得其职者也。此殆周礼泉府之遗制。而自夫用钱以后。中
之理也。故斲木为室。凝土为器。顺其性也。以釜甑爨。以铁耕。当其职也。其用器也亦然。上古只用陶匏。其后质变而文。俭趍于华。始有簠簋俎豆瑚琏之制焉。簠簋竹也。俎豆木也。瑚琏玉也。未闻用金银铜锡焉。观乎制字可见矣。甑甗。煎食之器也。瓶罂。贮水之器也皆从瓦。觞觥觯。盛酒之器也而从角。杯棬碗。盛羹之器也而从木。举一可以反三。惟乐器尚声。彝鼎铭功。故不得不用铜。而至于釜铛之属。则从金而多用铁耳。后世侈靡。或用金银之器。而未尝用铜。中国之俗。至今如此。臣之是行。观乎闾店市肆。器皆用磁。而不见铜锡。至如皇帝宴卓玉斝金罍。非不烂然。而饼果胾羹之盛。只是磁与铅耳。此其故何哉。窃尝思之。盖由铜以铸钱故也。夫钱者。百货之源。生民之命脉。一有所缺。则民国受其病。故收天下之铜。悉归之司农水衡。鼓铸不穷。然后可以运万货之权。尽四海之利也。是以惜之甚于金银。宝之加于珠玉。珠玉金银。入于舆马冠佩之饰。而一寸之铜。不得他用。试以新颁聚珍板序观之。至于销毁活字。付之宝源。则其计岂不长。其法岂不严乎。是谓顺生物之性。而各得其职者也。此殆周礼泉府之遗制。而自夫用钱以后。中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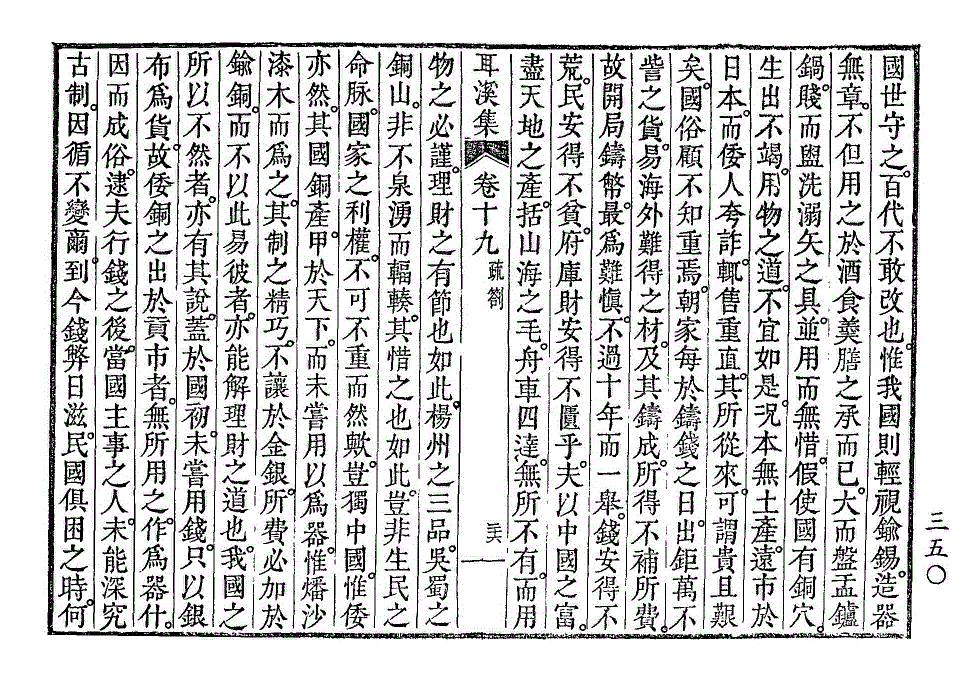 国世守之。百代不敢改也。惟我国则轻视鍮锡。造器无章。不但用之于酒食羹膳之承而已。大而盘盂炉锅。贱而盥洗溺矢之具。并用而无惜。假使国有铜穴。生出不竭。用物之道。不宜如是。况本无土产。远市于日本。而倭人夸诈。辄售重直。其所从来。可谓贵且艰矣。国俗顾不知重焉。朝家每于铸钱之日。出钜万不訾之货。易海外难得之材。及其铸成。所得不补所费。故开局铸币。最为难慎。不过十年而一举。钱安得不荒。民安得不贫。府库财安得不匮乎。夫以中国之富。尽天地之产。括山海之毛。舟车四达。无所不有。而用物之必谨。理财之有节也如此。杨州之三品。吴蜀之铜山。非不泉涌而辐辏。其惜之也如此。岂非生民之命脉。国家之利权。不可不重而然欤。岂独中国。惟倭亦然。其国铜产。甲于天下。而未尝用以为器。惟燔沙漆木而为之。其制之精巧。不让于金银。所费必加于鍮铜。而不以此易彼者。亦能解理财之道也。我国之所以不然者。亦有其说。盖于国初。未尝用钱。只以银布为货。故倭铜之出于贡市者。无所用之。作为器什。因而成俗。逮夫行钱之后。当国主事之人。未能深究古制。因循不变尔。到今钱弊日滋。民国俱困之时。何
国世守之。百代不敢改也。惟我国则轻视鍮锡。造器无章。不但用之于酒食羹膳之承而已。大而盘盂炉锅。贱而盥洗溺矢之具。并用而无惜。假使国有铜穴。生出不竭。用物之道。不宜如是。况本无土产。远市于日本。而倭人夸诈。辄售重直。其所从来。可谓贵且艰矣。国俗顾不知重焉。朝家每于铸钱之日。出钜万不訾之货。易海外难得之材。及其铸成。所得不补所费。故开局铸币。最为难慎。不过十年而一举。钱安得不荒。民安得不贫。府库财安得不匮乎。夫以中国之富。尽天地之产。括山海之毛。舟车四达。无所不有。而用物之必谨。理财之有节也如此。杨州之三品。吴蜀之铜山。非不泉涌而辐辏。其惜之也如此。岂非生民之命脉。国家之利权。不可不重而然欤。岂独中国。惟倭亦然。其国铜产。甲于天下。而未尝用以为器。惟燔沙漆木而为之。其制之精巧。不让于金银。所费必加于鍮铜。而不以此易彼者。亦能解理财之道也。我国之所以不然者。亦有其说。盖于国初。未尝用钱。只以银布为货。故倭铜之出于贡市者。无所用之。作为器什。因而成俗。逮夫行钱之后。当国主事之人。未能深究古制。因循不变尔。到今钱弊日滋。民国俱困之时。何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1H 页
 可不变而通之乎。臣谓国中鍮铜之物。祭器乐器外。一切禁绝。限以时月。使之输官。计还其直。则民无骚扰之弊。国有永久之利。而代用之器。不患无物矣。通一国鍮铜之器。可以亿万斤计。而所偿之价。必不及远易倭市之费。藏之度支。以之铸钱。则国用自裕。铜直自轻矣。且观中国之法。不但铜也。惟铁亦不妄用。农器之外。虽于宫室之构。专用土木。用铁至少者。盖以铁是兵器之材也。栏槛厅壁。皆需瓦甓。盘盒匮箧。多用纸皮。用木至少者。盖以木是舟车之材也。笔管烟茎。亦用芦藤。而不用竹者。盖以竹是箭弩之材也。此皆中国理财之法。古今相传之秘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国安得不富。民安得不阜。兵安得不强耶。至于耕织碓硙之具。笔墨胶漆之类。亦是生民日用之不可阙者。而简易精利。皆有自然之巧。不易之矩。经曰。智者刱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岂不信欤。中国者。圣人之旧居也。制作之妙。所由来远矣。臣于禁铜之制。窃有推类而默契者。并此附陈焉。谋国计者。皆不可不知也。
可不变而通之乎。臣谓国中鍮铜之物。祭器乐器外。一切禁绝。限以时月。使之输官。计还其直。则民无骚扰之弊。国有永久之利。而代用之器。不患无物矣。通一国鍮铜之器。可以亿万斤计。而所偿之价。必不及远易倭市之费。藏之度支。以之铸钱。则国用自裕。铜直自轻矣。且观中国之法。不但铜也。惟铁亦不妄用。农器之外。虽于宫室之构。专用土木。用铁至少者。盖以铁是兵器之材也。栏槛厅壁。皆需瓦甓。盘盒匮箧。多用纸皮。用木至少者。盖以木是舟车之材也。笔管烟茎。亦用芦藤。而不用竹者。盖以竹是箭弩之材也。此皆中国理财之法。古今相传之秘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国安得不富。民安得不阜。兵安得不强耶。至于耕织碓硙之具。笔墨胶漆之类。亦是生民日用之不可阙者。而简易精利。皆有自然之巧。不易之矩。经曰。智者刱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岂不信欤。中国者。圣人之旧居也。制作之妙。所由来远矣。臣于禁铜之制。窃有推类而默契者。并此附陈焉。谋国计者。皆不可不知也。五曰罢毡帽。夫交邻互市之法。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欲其两利而俱便。可久而无弊焉耳。宋与夏市。以茶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1L 页
 易马。元昊尚幼。谏其父勿许。当时识者。忧其为他日患。亦可见互市之不可不慎也。今我西北之市。便同贡献。固不可较挈多寡。而至于使行时商译交贸。则一从和买之例。不可不计其得失也。我国所挟之货。惟银为长物。而前时倭银通行。将此入燕。既去复来。如环之转。故虽有物货之贵贱。贸迁之输赢。而本国自无所失矣。挽近以来。倭银路绝。代送矿银。是则一渡鸭水。永不还来。殆同投金于渊。非计之得也。以故国中之银货日耗。试以臣行言之。员译包银。太半空虚。商货之枯涸。可推而知。为今之计。政宜稍节入北之银。以备逐岁之赀。而盘缠公用。不可减也。译员定额。不可缺也。无宁就其交贸之物。换来实用之需。则犹不失互市之本意矣。惟是帽子一物。最为无用之费。耗国漏财。莫甚于此。不可不急塞其孔也。盖帽子者。经史之所不载。天下之所未有。而独我国用之。男子则冠上加冠。已失礼意。妇人则非笄非巾。实为无稽。不过为御寒之资而已。只为御寒。岂无他物。而何必远求于异国乎。中国则无所用之。故辽商一肆。聚毛打造。专售我国。坐收大利。岂不为华人之所笑乎。一年帽价。动费钜万。以不訾之活货。易无用之毳物。
易马。元昊尚幼。谏其父勿许。当时识者。忧其为他日患。亦可见互市之不可不慎也。今我西北之市。便同贡献。固不可较挈多寡。而至于使行时商译交贸。则一从和买之例。不可不计其得失也。我国所挟之货。惟银为长物。而前时倭银通行。将此入燕。既去复来。如环之转。故虽有物货之贵贱。贸迁之输赢。而本国自无所失矣。挽近以来。倭银路绝。代送矿银。是则一渡鸭水。永不还来。殆同投金于渊。非计之得也。以故国中之银货日耗。试以臣行言之。员译包银。太半空虚。商货之枯涸。可推而知。为今之计。政宜稍节入北之银。以备逐岁之赀。而盘缠公用。不可减也。译员定额。不可缺也。无宁就其交贸之物。换来实用之需。则犹不失互市之本意矣。惟是帽子一物。最为无用之费。耗国漏财。莫甚于此。不可不急塞其孔也。盖帽子者。经史之所不载。天下之所未有。而独我国用之。男子则冠上加冠。已失礼意。妇人则非笄非巾。实为无稽。不过为御寒之资而已。只为御寒。岂无他物。而何必远求于异国乎。中国则无所用之。故辽商一肆。聚毛打造。专售我国。坐收大利。岂不为华人之所笑乎。一年帽价。动费钜万。以不訾之活货。易无用之毳物。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2H 页
 甫经秋冬。弊而投地。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山川之宝藏有限。天下之毡毛无尽。将何以继之乎。臣谓亟罢帽子之贸。仍下国中之禁。而入燕之包。代贸有用之物。如骡马布绢之类。则庶有补于利用厚生之具。而日计不足。岁计有馀矣。至于帽税之充补公用。稍为通变之端。惟在庙堂之商确区划耳。
甫经秋冬。弊而投地。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山川之宝藏有限。天下之毡毛无尽。将何以继之乎。臣谓亟罢帽子之贸。仍下国中之禁。而入燕之包。代贸有用之物。如骡马布绢之类。则庶有补于利用厚生之具。而日计不足。岁计有馀矣。至于帽税之充补公用。稍为通变之端。惟在庙堂之商确区划耳。六曰肄华语。夫汉人之语。即中华之正音也。一自晋代以后。五胡交乱。方言屡变。字音亦讹。而犹可因其似而求其真矣。我国之音。最近于中国。而罗丽以来。既无翻解之方。每患通习之难矣。惟我 世宗大王睿智出天。独运神机。刱造训民正音。质诸华人。曲尽微妙。凡四方之言语。万窍之声籁。皆可形容于笔端。虽街童巷妇。亦能通晓。开物成务之功。可谓发前圣之未发。而参天地之造化矣。以此翻出汉音。迎刃缕解。于以谐字韵。于以叶声律。故当时士大夫多通华语。奉使迎诏之时。不假译舌。酬答如响。及至壬癸之际。如乞灵卞诬。国之大事。多赖其力。华语之不可不习也如此。近世以来。汉学之讲。便成文具。能通句读者绝少。故使臣之与彼相对也。耳袖而口噤。片言单辞。专仗象胥。所谓象胥。亦仅解街巷例话而已。将何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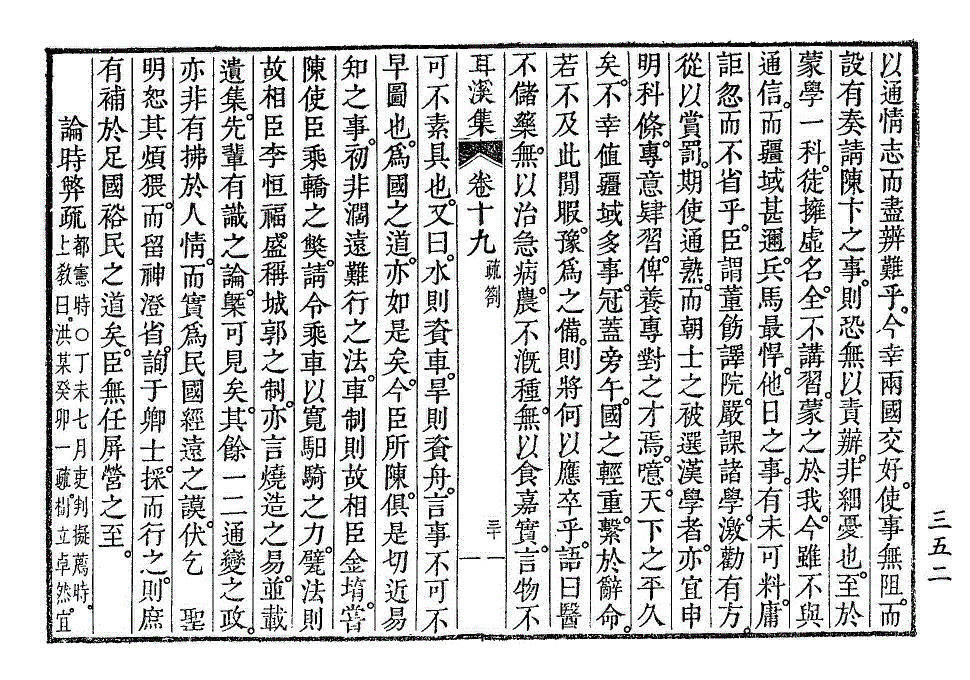 以通情志而尽辨难乎。今幸两国交好。使事无阻。而设有奏请陈卞之事。则恐无以责辨。非细忧也。至于蒙学一科。徒拥虚名。全不讲习。蒙之于我。今虽不与通信。而疆域甚迩。兵马最悍。他日之事。有未可料。庸讵忽而不省乎。臣谓董饬译院。严课诸学。激劝有方。从以赏罚。期使通熟。而朝士之被选汉学者。亦宜申明科条。专意肄习。俾养专对之才焉。噫。天下之平久矣。不幸值疆域多事。冠盖旁午。国之轻重。系于辞命。若不及此閒暇。豫为之备。则将何以应卒乎。语曰医不储药。无以治急病。农不溉种。无以食嘉实。言物不可不素具也。又曰。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言事不可不早图也。为国之道。亦如是矣。今臣所陈。俱是切近易知之事。初非阔远难行之法。车制则故相臣金堉。尝陈使臣乘轿之弊。请令乘车以宽驲骑之力。甓法则故相臣李恒福。盛称城郭之制。亦言烧造之易。并载遗集。先辈有识之论。槩可见矣。其馀一二通变之政。亦非有拂于人情。而实为民国经远之谟。伏乞 圣明恕其烦猥。而留神澄省。询于卿士。采而行之。则庶有补于足国裕民之道矣。臣无任屏营之至。
以通情志而尽辨难乎。今幸两国交好。使事无阻。而设有奏请陈卞之事。则恐无以责辨。非细忧也。至于蒙学一科。徒拥虚名。全不讲习。蒙之于我。今虽不与通信。而疆域甚迩。兵马最悍。他日之事。有未可料。庸讵忽而不省乎。臣谓董饬译院。严课诸学。激劝有方。从以赏罚。期使通熟。而朝士之被选汉学者。亦宜申明科条。专意肄习。俾养专对之才焉。噫。天下之平久矣。不幸值疆域多事。冠盖旁午。国之轻重。系于辞命。若不及此閒暇。豫为之备。则将何以应卒乎。语曰医不储药。无以治急病。农不溉种。无以食嘉实。言物不可不素具也。又曰。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言事不可不早图也。为国之道。亦如是矣。今臣所陈。俱是切近易知之事。初非阔远难行之法。车制则故相臣金堉。尝陈使臣乘轿之弊。请令乘车以宽驲骑之力。甓法则故相臣李恒福。盛称城郭之制。亦言烧造之易。并载遗集。先辈有识之论。槩可见矣。其馀一二通变之政。亦非有拂于人情。而实为民国经远之谟。伏乞 圣明恕其烦猥。而留神澄省。询于卿士。采而行之。则庶有补于足国裕民之道矣。臣无任屏营之至。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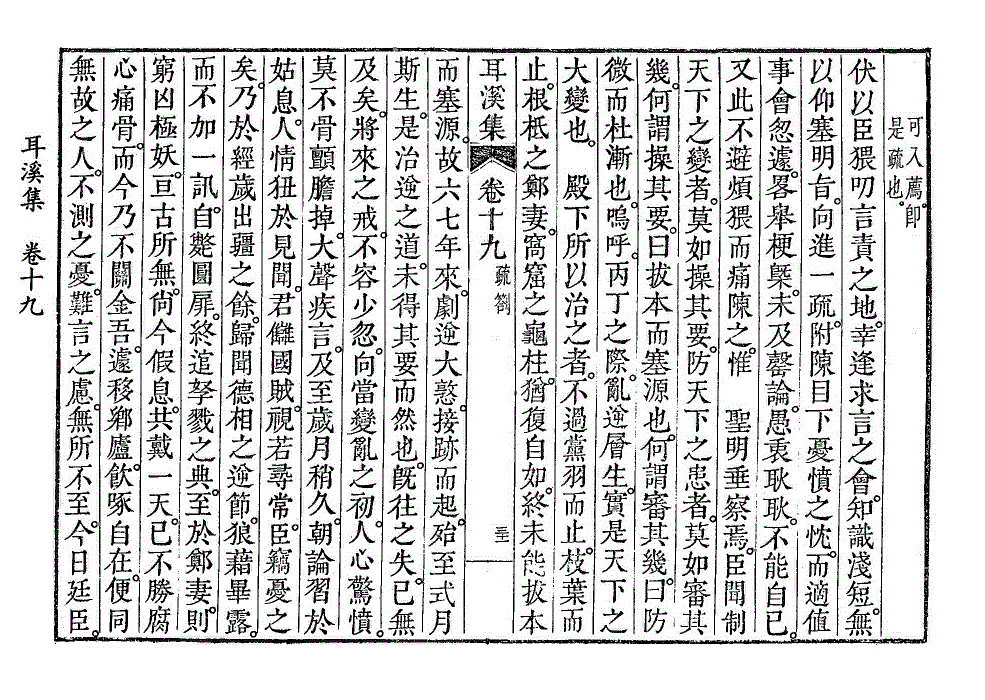 论时弊疏(都宪时○丁未七月吏判拟荐时。 上教曰。洪某癸卯一疏。树立卓然。宜可入荐。即是疏也。)
论时弊疏(都宪时○丁未七月吏判拟荐时。 上教曰。洪某癸卯一疏。树立卓然。宜可入荐。即是疏也。)伏以臣猥叨言责之地。幸逢求言之会。知识浅短。无以仰塞明旨。向进一疏。附陈目下忧愤之忱。而适值事会匆遽。略举梗槩。未及罄论。愚衷耿耿。不能自已。又此不避烦猥而痛陈之。惟 圣明垂察焉。臣闻制天下之变者。莫如操其要。防天下之患者。莫如审其几。何谓操其要。曰拔本而塞源也。何谓审其几。曰防微而杜渐也。呜呼。丙丁之际。乱逆层生。实是天下之大变也。 殿下所以治之者。不过党羽而止。枝叶而止。根柢之郑妻。窝窟之龟柱。犹复自如。终未能拔本而塞源。故六七年来。剧逆大熟。接迹而起。殆至式月斯生。是治逆之道。未得其要而然也。既往之失。已无及矣。将来之戒。不容少忽。向当变乱之初。人心惊愤。莫不骨颤胆掉。大声疾言。及至岁月稍久。朝论习于姑息。人情狃于见闻。君雠国贼。视若寻常。臣窃忧之矣。乃于经岁出疆之馀。归闻德相之逆节。狼藉毕露。而不加一讯。自毙圆扉。终逭孥戮之典。至于郑妻。则穷凶极妖。亘古所无。尚今假息。共戴一天。已不胜腐心痛骨。而今乃不关金吾。遽移乡庐。饮啄自在。便同无故之人。不测之忧。难言之虑。无所不至。今日廷臣。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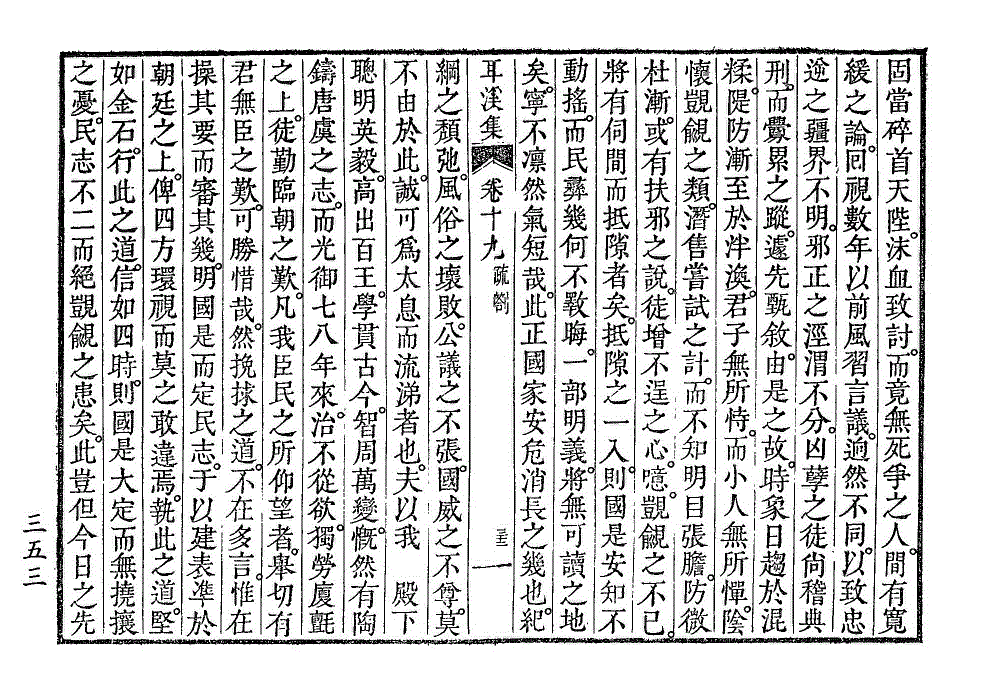 固当碎首天陛。沫血致讨。而竟无死争之人。间有宽缓之论。回视数年以前风习言议。迥然不同。以致忠逆之疆界不明。邪正之泾渭不分。凶孽之徒尚稽典刑。而衅累之踪。遽先甄叙。由是之故。时象日趋于混糅。堤防渐至于泮涣。君子无所恃。而小人无所惮。阴怀觊觎之类。潜售尝试之计。而不知明目张胆。防微杜渐。或有扶邪之说。徒增不逞之心。噫。觊觎之不已。将有伺间而抵隙者矣。抵隙之一入。则国是安知不动摇。而民彝几何不斁晦。一部明义。将无可读之地矣。宁不凛然气短哉。此正国家安危消长之几也。纪纲之颓弛。风俗之坏败。公议之不张。国威之不尊。莫不由于此。诚可为太息而流涕者也。夫以我 殿下聪明英毅。高出百王。学贯古今。智周万变。慨然有陶铸唐虞之志。而光御七八年来。治不从欲。独劳厦毡之上。徒勤临朝之叹。凡我臣民之所仰望者。举切有君无臣之叹。可胜惜哉。然挽救之道。不在多言。惟在操其要而审其几。明国是而定民志。于以建表准于朝廷之上。俾四方环视而莫之敢违焉。执此之道。坚如金石。行此之道。信如四时。则国是大定而无挠攘之忧。民志不二而绝觊觎之患矣。此岂但今日之先
固当碎首天陛。沫血致讨。而竟无死争之人。间有宽缓之论。回视数年以前风习言议。迥然不同。以致忠逆之疆界不明。邪正之泾渭不分。凶孽之徒尚稽典刑。而衅累之踪。遽先甄叙。由是之故。时象日趋于混糅。堤防渐至于泮涣。君子无所恃。而小人无所惮。阴怀觊觎之类。潜售尝试之计。而不知明目张胆。防微杜渐。或有扶邪之说。徒增不逞之心。噫。觊觎之不已。将有伺间而抵隙者矣。抵隙之一入。则国是安知不动摇。而民彝几何不斁晦。一部明义。将无可读之地矣。宁不凛然气短哉。此正国家安危消长之几也。纪纲之颓弛。风俗之坏败。公议之不张。国威之不尊。莫不由于此。诚可为太息而流涕者也。夫以我 殿下聪明英毅。高出百王。学贯古今。智周万变。慨然有陶铸唐虞之志。而光御七八年来。治不从欲。独劳厦毡之上。徒勤临朝之叹。凡我臣民之所仰望者。举切有君无臣之叹。可胜惜哉。然挽救之道。不在多言。惟在操其要而审其几。明国是而定民志。于以建表准于朝廷之上。俾四方环视而莫之敢违焉。执此之道。坚如金石。行此之道。信如四时。则国是大定而无挠攘之忧。民志不二而绝觊觎之患矣。此岂但今日之先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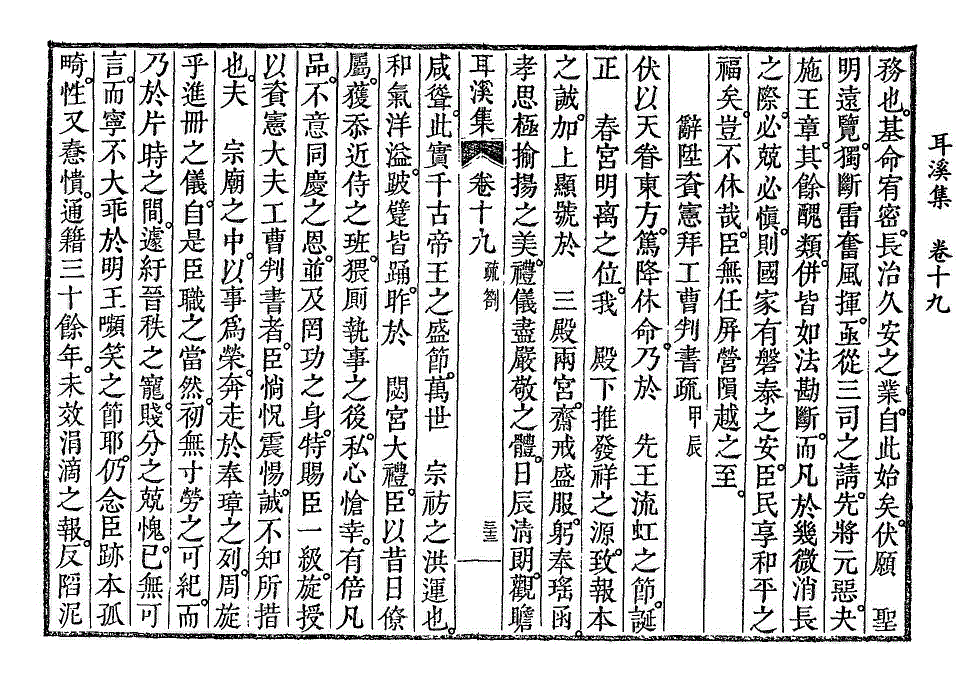 务也。基命宥密。长治久安之业。自此始矣。伏愿圣明远览。独断雷奋风挥。亟从三司之请。先将元恶。夬施王章。其馀丑类。并皆如法勘断。而凡于几微消长之际。必兢必慎。则国家有磐泰之安。臣民享和平之福矣。岂不休哉。臣无任屏营陨越之至。
务也。基命宥密。长治久安之业。自此始矣。伏愿圣明远览。独断雷奋风挥。亟从三司之请。先将元恶。夬施王章。其馀丑类。并皆如法勘断。而凡于几微消长之际。必兢必慎。则国家有磐泰之安。臣民享和平之福矣。岂不休哉。臣无任屏营陨越之至。辞升资宪拜工曹判书疏(甲辰)
伏以天眷东方。笃降休命。乃于 先王流虹之节。诞正 春宫明离之位。我 殿下推发祥之源。致报本之诚。加上显号于 三殿两宫。斋戒盛服。躬奉瑶函。孝思极揄扬之美。礼仪尽严敬之体。日辰清朗。观瞻咸耸。此实千古帝王之盛节。万世 宗祊之洪运也。和气洋溢。跛躄皆踊。昨于 閟宫大礼。臣以昔日僚属。获忝近侍之班。猥厕执事之后。私心怆幸。有倍凡品。不意同庆之恩。并及罔功之身。特赐臣一级。旋授以资宪大夫工曹判书者。臣惝恍震惕。诚不知所措也。夫 宗庙之中。以事为荣。奔走于奉璋之列。周旋乎进册之仪。自是臣职之当然。初无寸劳之可纪。而乃于片时之间。遽纡晋秩之宠。贱分之兢愧。已无可言。而宁不大乖于明王嚬笑之节耶。仍念臣迹本孤畸。性又憃愦。通籍三十馀年。未效涓滴之报。反陷泥
耳溪集卷十九 第 354L 页
 涂之中。惟 圣明拯拔之薰沐之。复齿于任使之末。恩除联翩。眷顾隆厚。臣铭在心腑。矢死图报。职无閒剧。事无夷病。惟思随分而尽力。未尝饰让而图便。庶圣鉴俯烛之矣。顾玆九卿之职。古称槐棘之班。望峻责钜。不比庶官。固非循资积功之所可致。岂宜用之为酬劳之具。况无可酬之劳者乎。如是而上不难于轻授。下不惮于冒承。则名器于是乎益轻。而朝廷于是乎不尊。可不惧哉。玆敢据实自列。仰渎崇听。伏乞圣明亟命收还臣新授职秩。使爵赏无滥而私分获安。不胜幸甚。
涂之中。惟 圣明拯拔之薰沐之。复齿于任使之末。恩除联翩。眷顾隆厚。臣铭在心腑。矢死图报。职无閒剧。事无夷病。惟思随分而尽力。未尝饰让而图便。庶圣鉴俯烛之矣。顾玆九卿之职。古称槐棘之班。望峻责钜。不比庶官。固非循资积功之所可致。岂宜用之为酬劳之具。况无可酬之劳者乎。如是而上不难于轻授。下不惮于冒承。则名器于是乎益轻。而朝廷于是乎不尊。可不惧哉。玆敢据实自列。仰渎崇听。伏乞圣明亟命收还臣新授职秩。使爵赏无滥而私分获安。不胜幸甚。耳溪集卷十九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