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耳溪集卷十七 第 x 页
耳溪集卷十七
铭
铭
耳溪集卷十七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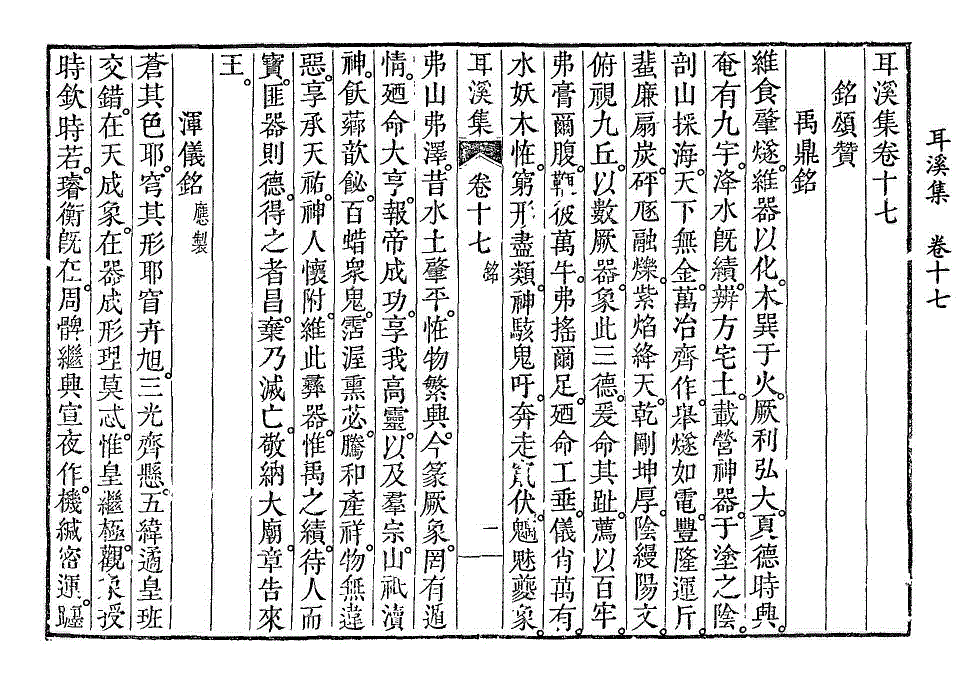 禹鼎铭
禹鼎铭维食肇燧。维器以化。木巽于火。厥利弘大。夏德时兴。奄有九宇。洚水既绩。辨方宅土。载营神器。于涂之阴。剖山采海。天下无金。万冶齐作。举燧如电。丰隆运斤。蜚廉扇炭。砰豗融烁。紫焰绛天。乾刚坤厚。阴缦阳文。俯视九丘。以数厥器。象此三德。爰命其趾。荐以百牢。弗膏尔腹。鞭彼万牛。弗摇尔足。乃命工垂。仪肖万有。水妖木怪。穷形尽类。神骇鬼吁。奔走窜伏。魑魅夔象。弗山弗泽。昔水土肇平。怪物繁兴。今篆厥象。罔有遁情。乃命大亨。报帝成功。享我高灵。以及群宗。山祇渎神。饫芗歆飶。百蜡众鬼。沾渥熏苾。腾和产祥。物无违恶。享承天祐。神人怀附。维此彝器。惟禹之绩。待人而宝。匪器则德。得之者昌。弃乃灭亡。敬纳大庙。章告来王。
浑仪铭(应制)
苍其色耶。穹其形耶窅卉旭。三光齐悬。五纬遹皇班交错。在天成象。在器成形理莫忒。惟皇继极。观象授时钦时若。璿衡既在。周髀继兴宣夜作。机缄密运。躔
耳溪集卷十七 第 2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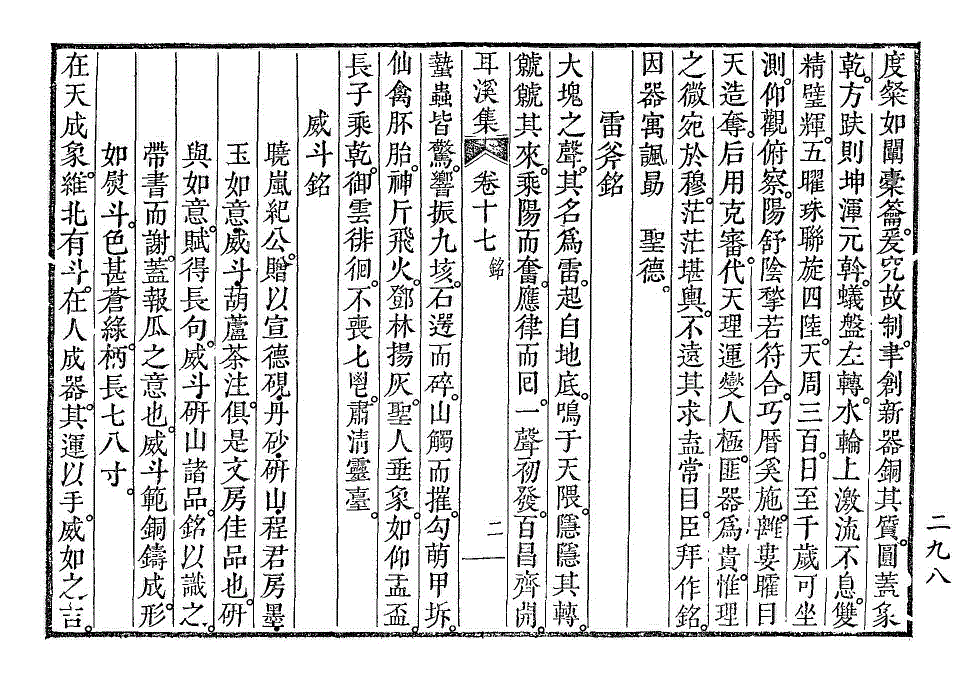 度粲如阐橐籥。爰究故制。聿创新器铜其质。圆盖象乾。方趺则坤浑元斡。蚁盘左转。水轮上激流不息。双精璧辉。五曜珠联旋四陆。天周三百。日至千岁可坐测。仰观俯察。阳舒阴揫若符合。巧历奚施。离娄矐目天造夺。后用克审。代天理运燮人极。匪器为贵。惟理之微宛于穆。茫茫堪舆。不远其求盍常目。臣拜作铭。因器寓讽勖 圣德。
度粲如阐橐籥。爰究故制。聿创新器铜其质。圆盖象乾。方趺则坤浑元斡。蚁盘左转。水轮上激流不息。双精璧辉。五曜珠联旋四陆。天周三百。日至千岁可坐测。仰观俯察。阳舒阴揫若符合。巧历奚施。离娄矐目天造夺。后用克审。代天理运燮人极。匪器为贵。惟理之微宛于穆。茫茫堪舆。不远其求盍常目。臣拜作铭。因器寓讽勖 圣德。雷斧铭
大块之声。其名为雷。起自地底。鸣于天隈。隐隐其转。虩虩其来。乘阳而奋。应律而回。一声初发。百昌齐开。蛰虫皆惊。响振九垓。仁遌而碎。山触而摧。勾萌甲坼。仙禽胚胎。神斤飞火。邓林扬灰。圣人垂象。如仰盂杯。长子乘乾。御云徘徊。不丧匕鬯。肃清灵台。
威斗铭
晓岚纪公。赠以宣德砚,丹砂,研山,程君房墨,玉如意,威斗,葫芦茶注。俱是文房佳品也。研与如意。赋得长句。威斗,研山诸品。铭以识之。带书而谢。盖报瓜之意也。威斗范铜铸成。形如熨斗。色甚苍绿。柄长七八寸。
在天成象。维北有斗。在人成器。其运以手。威如之吉。
耳溪集卷十七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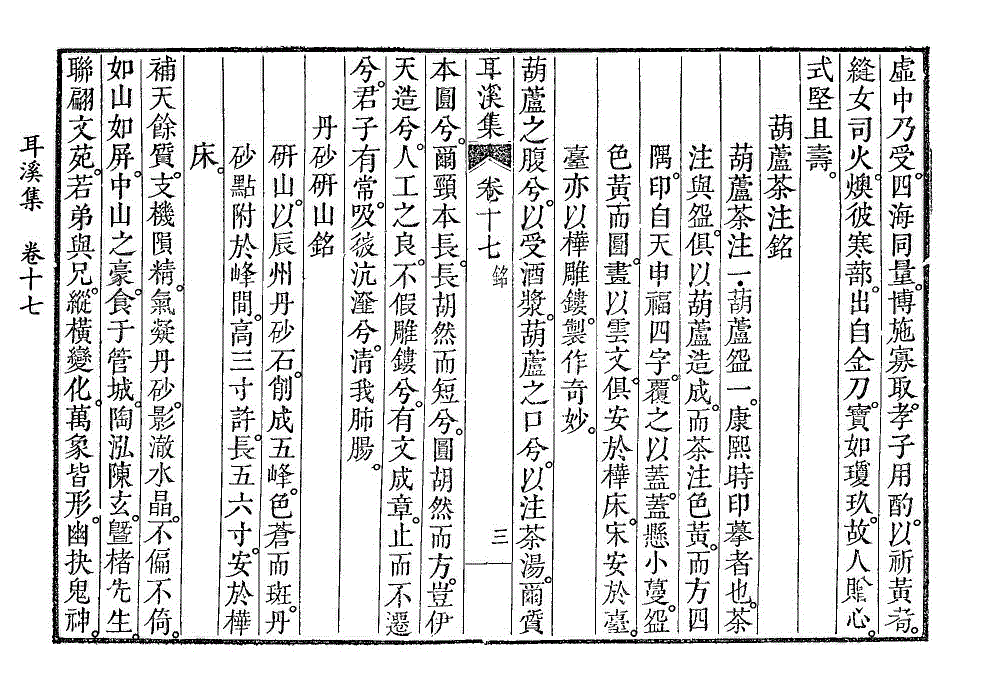 虚中乃受。四海同量。博施寡取。孝子用酌。以祈黄耇。缝女司火。燠彼寒蔀。出自金刀。宝如琼玖。故人赠心。式坚且寿。
虚中乃受。四海同量。博施寡取。孝子用酌。以祈黄耇。缝女司火。燠彼寒蔀。出自金刀。宝如琼玖。故人赠心。式坚且寿。葫芦茶注铭
葫芦茶注一,葫芦碗一。康熙时印摹者也。茶注与碗。俱以葫芦造成。而茶注色黄。而方四隅。印自天申福四字。覆之以盖。盖悬小蔓。碗色黄而圆。画以云文。俱安于桦床。宋安于台。台亦以桦雕镂。制作奇妙。
葫芦之腹兮。以受酒浆。葫芦之口兮。以注茶汤。尔质本圆兮。尔颈本长。长胡然而短兮。圆胡然而方。岂伊天造兮。人工之良。不假雕镂兮。有文成章。止而不迁兮。君子有常。吸彼沆瀣兮。清我肺肠。
丹砂研山铭
研山。以辰州丹砂石。削成五峰。色苍而斑。丹砂点附于峰间。高三寸许。长五六寸。安于桦床。
补天馀质。支机陨精。气凝丹砂。影澈水晶。不偏不倚。如山如屏。中山之豪。食于管城。陶泓陈玄。暨楮先生。联翩文苑。若弟与兄。纵横变化。万象皆形。幽抉鬼神。
耳溪集卷十七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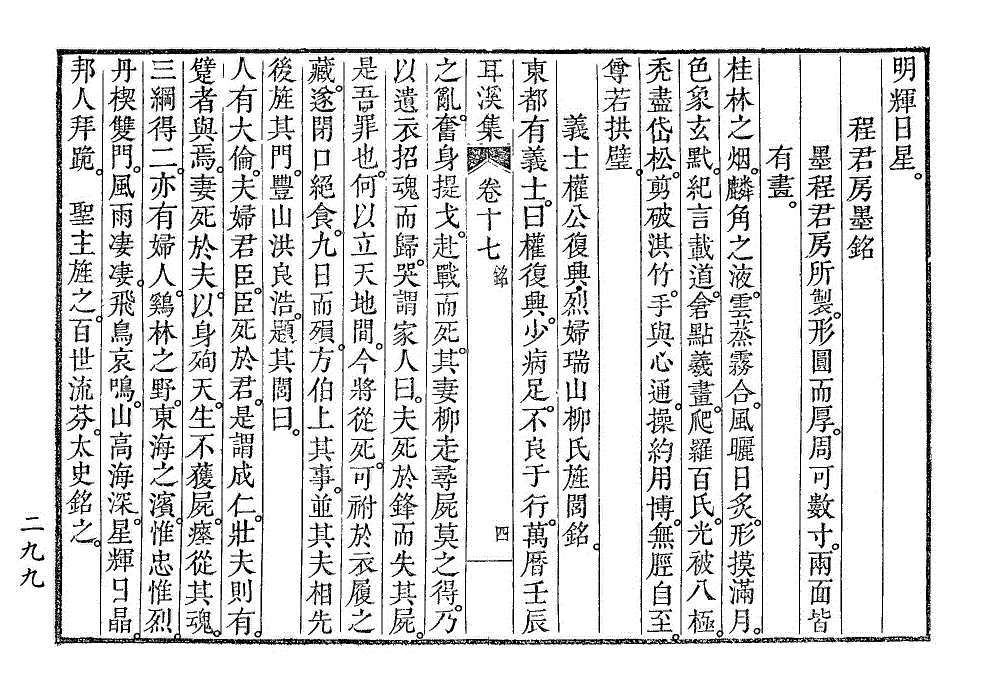 明辉日星。
明辉日星。程君房墨铭
墨程君房所制。形圆而厚。周可数寸。两面皆有画。
桂林之烟。麟角之液。云蒸雾合。风晒日炙。形摸满月。色象玄黓。纪言载道。仓点羲画。爬罗百氏。光被八极。秃尽岱松。剪破淇竹。手与心通。操约用博。无胫自至。尊若拱璧。
义士权公复兴,烈妇瑞山柳氏旌闾铭。
东都有义士。曰权复兴。少病足。不良于行。万历壬辰之乱。奋身提戈。赴战而死。其妻柳走寻尸莫之得。乃以遗衣招魂而归。哭谓家人曰。夫死于锋而失其尸。是吾罪也。何以立天地间。今将从死。可祔于衣履之藏。遂闭口绝食。九日而殒。方伯上其事。并其夫相先后旌其门。丰山洪良浩。题其闾曰。
人有大伦。夫妇君臣。臣死于君。是谓成仁。壮夫则有。躄者与焉。妻死于夫。以身殉天。生不获尸。瘗从其魂。三纲得二。亦有妇人。鸡林之野。东海之滨。惟忠惟烈。丹楔双门。风雨凄凄。飞鸟哀鸣。山高海深。星辉日晶。邦人拜跪。 圣主旌之。百世流芬。太史铭之。
耳溪集卷十七
颂
赠冠颂
活山居士夜失冠。不能出门。太守闻之。赠以新冠。为文以祝之。居士即南上舍龙万也。
古有窃屦。今闻窃冠。屦或可阙。冠不可删。不屦曰跣。无冠曰免。君子可跣。而不可免。何不易之以端冕。星星白发。元服是加。勉尔德之日新兮。共此冠而峨峨。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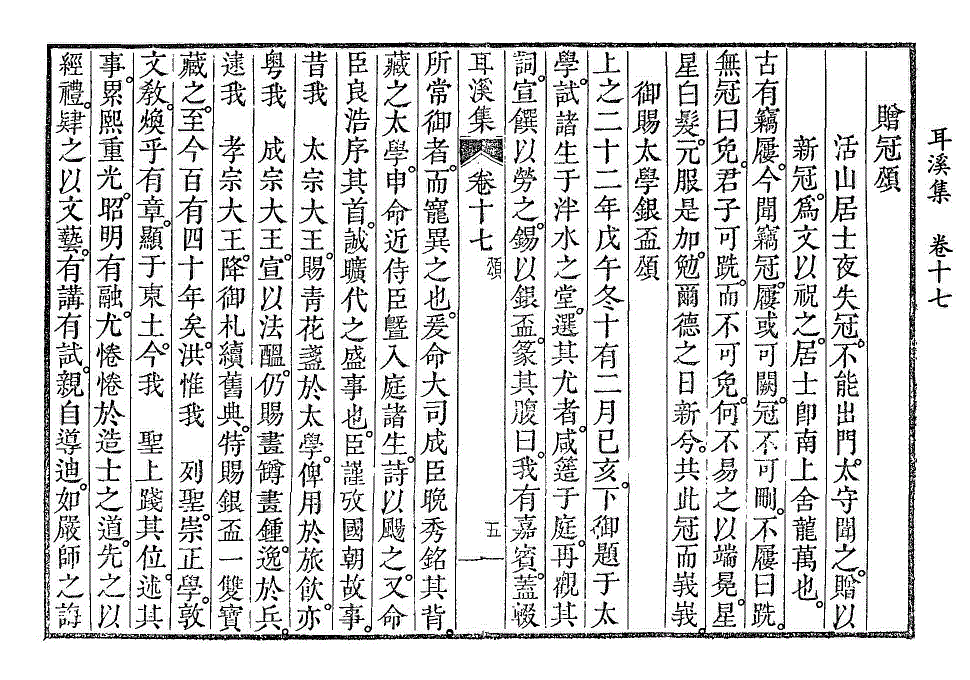 御赐太学银杯颂
御赐太学银杯颂上之二十二年戊午冬十有二月己亥。下御题于太学。试诸生于泮水之堂。选其尤者。咸簉于庭。再观其词。宣馔以劳之。锡以银杯。篆其腹曰。我有嘉宾。盖辍所常御者。而宠异之也。爰命大司成臣晚秀铭其背。藏之太学。申命近侍臣暨入庭诸生。诗以飏之。又命臣良浩序其首。诚旷代之盛事也。臣谨考国朝故事。昔我 太宗大王。赐青花盏于太学。俾用于旅饮。亦粤我 成宗大王。宣以法酝。仍赐画樽画钟。逸于兵。逮我 孝宗大王。降御札续旧典。特赐银杯一双宝藏之。至今百有四十年矣。洪惟我 列圣。崇正学。敦文教。焕乎有章。显于东土。今我 圣上践其位。述其事。累熙重光。昭明有融。尤惓惓于造士之道。先之以经礼。肄之以文艺。有讲有试。亲自导迪。如严师之诲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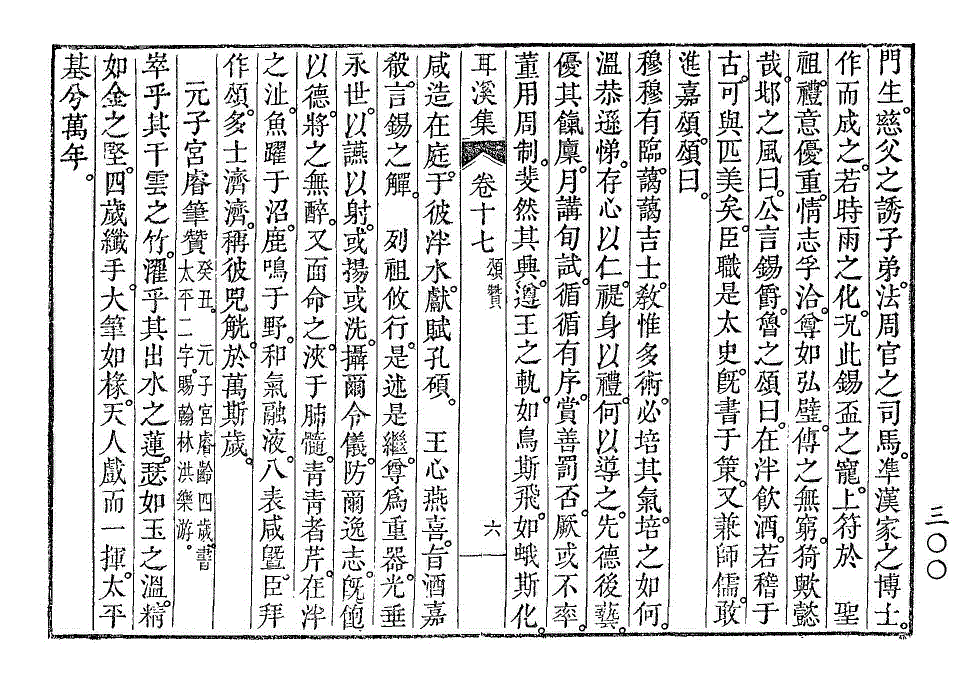 门生。慈父之诱子弟。法周官之司马。准汉家之博士。作而成之。若时雨之化。况此锡杯之宠。上符于 圣祖。礼意优重。情志孚洽。尊如弘璧。传之无穷。猗欤懿哉。邶之风曰。公言锡爵。鲁之颂曰。在泮饮酒。若稽于古。可与匹美矣。臣职是太史。既书于策。又兼师儒。敢进嘉颂。颂曰。
门生。慈父之诱子弟。法周官之司马。准汉家之博士。作而成之。若时雨之化。况此锡杯之宠。上符于 圣祖。礼意优重。情志孚洽。尊如弘璧。传之无穷。猗欤懿哉。邶之风曰。公言锡爵。鲁之颂曰。在泮饮酒。若稽于古。可与匹美矣。臣职是太史。既书于策。又兼师儒。敢进嘉颂。颂曰。穆穆有临。蔼蔼吉士。教惟多术。必培其气。培之如何。温恭逊悌。存心以仁。禔身以礼。何以导之。先德后艺。优其饩廪。月讲旬试。循循有序。赏善罚否。厥或不率。董用周制。斐然其兴。遵王之轨。如鸟斯飞。如蛾斯化。咸造在庭。于彼泮水。献赋孔硕。 王心燕喜。旨酒嘉殽。言锡之觯。 列祖攸行。是述是继。尊为重器。光垂永世。以宴以射。或扬或洗。摄尔令仪。防尔逸志。既饱以德。将之无醉。又面命之。浃于肺髓。青青者芹。在泮之沚。鱼跃于沼。鹿鸣于野。和气融液。八表咸暨。臣拜作颂。多士济济。称彼兕觥。于万斯岁。
耳溪集卷十七
赞
元子宫睿笔赞(癸丑。 元子宫睿龄四岁。书太平二字。赐翰林洪乐游。)
崒乎其干云之竹。濯乎其出水之莲。瑟如玉之温。精如金之坚。四岁纤手。大笔如椽。天人戏而一挥。太平基兮万年。
耳溪集卷十七
辨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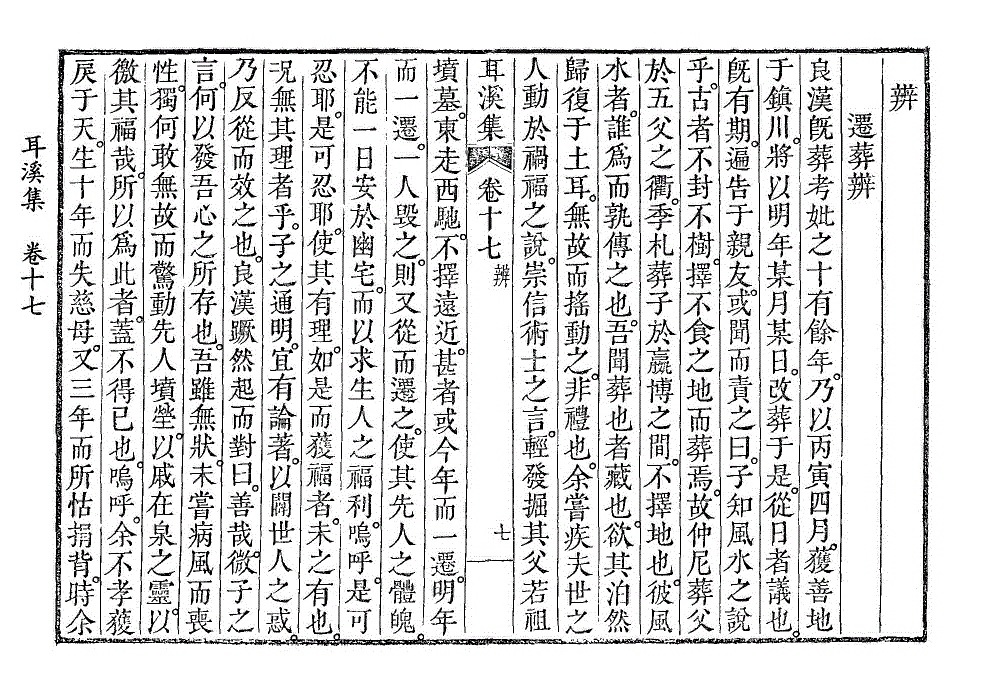 迁葬辨
迁葬辨良汉既葬考妣之十有馀年。乃以丙寅四月。获善地于镇川。将以明年某月某日。改葬于是。从日者议也。既有期。遍告于亲友。或闻而责之曰。子知风水之说乎。古者不封不树。择不食之地而葬焉。故仲尼葬父于五父之衢。季札葬子于嬴博之间。不择地也。彼风水者。谁为而孰传之也。吾闻葬也者藏也。欲其泊然归复于土耳。无故而摇动之。非礼也。余尝疾夫世之人动于祸福之说。崇信术士之言。轻发掘其父若祖坟墓。东走西驰。不择远近。甚者或今年而一迁。明年而一迁。一人毁之。则又从而迁之。使其先人之体魄。不能一日安于幽宅。而以求生人之福利。呜呼。是可忍耶。是可忍耶。使其有理。如是而获福者。未之有也。况无其理者乎。子之通明。宜有论著。以辟世人之惑。乃反从而效之也。良汉蹶然起而对曰。善哉。微子之言。何以发吾心之所存也。吾虽无状。未尝病风而丧性。独何敢无故而惊动先人坟茔。以戚在泉之灵。以徼其福哉。所以为此者。盖不得已也。呜呼。余不孝获戾于天。生十年而失慈母。又三年而所怙捐背。时余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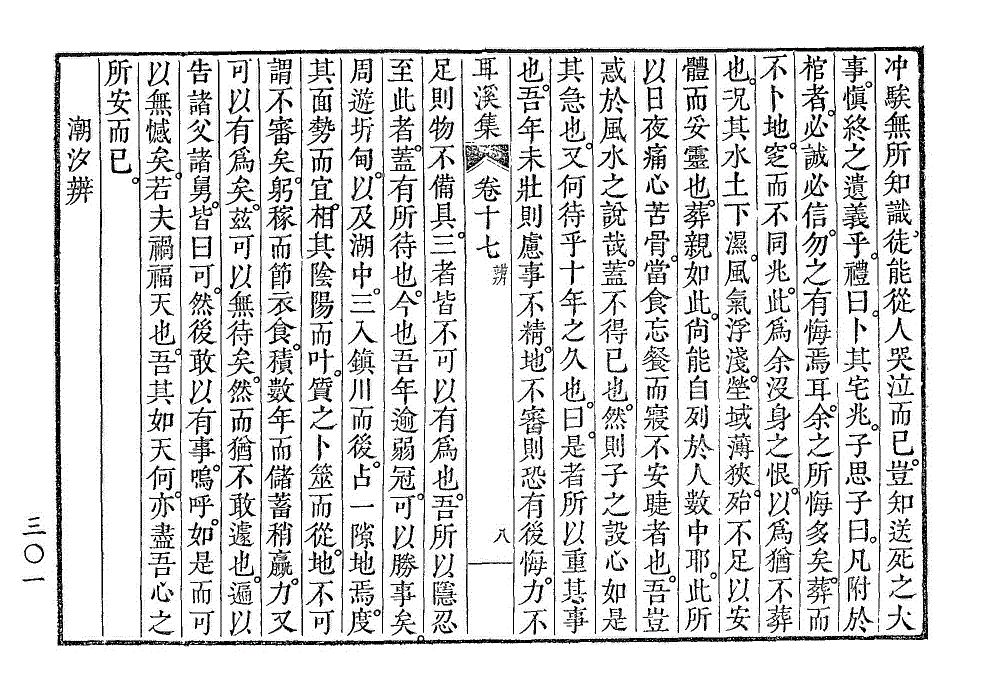 冲騃无所知识。徒能从人哭泣而已。岂知送死之大事。慎终之遗义乎。礼曰。卜其宅兆。子思子曰。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余之所悔多矣。葬而不卜地。窆而不同兆。此为余没身之恨。以为犹不葬也。况其水土下湿。风气浮浅。茔域薄狭。殆不足以安体而妥灵也。葬亲如此。尚能自列于人数中耶。此所以日夜痛心苦骨。当食忘餐而寝不安睫者也。吾岂惑于风水之说哉。盖不得已也。然则子之设心如是其急也。又何待乎十年之久也。曰。是者所以重其事也。吾年未壮则虑事不精。地不审则恐有后悔。力不足则物不备具。三者皆不可以有为也。吾所以隐忍至此者。盖有所待也。今也吾年逾弱冠。可以胜事矣。周游圻甸。以及湖中。三入镇川而后。占一隙地焉。度其面势而宜。相其阴阳而叶。质之卜筮而从。地不可谓不审矣。躬稼而节衣食。积数年而储蓄稍赢。力又可以有为矣。玆可以无待矣。然而犹不敢遽也。遍以告诸父诸舅。皆曰可。然后敢以有事。呜呼。如是而可以无憾矣。若夫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亦尽吾心之所安而已。
冲騃无所知识。徒能从人哭泣而已。岂知送死之大事。慎终之遗义乎。礼曰。卜其宅兆。子思子曰。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余之所悔多矣。葬而不卜地。窆而不同兆。此为余没身之恨。以为犹不葬也。况其水土下湿。风气浮浅。茔域薄狭。殆不足以安体而妥灵也。葬亲如此。尚能自列于人数中耶。此所以日夜痛心苦骨。当食忘餐而寝不安睫者也。吾岂惑于风水之说哉。盖不得已也。然则子之设心如是其急也。又何待乎十年之久也。曰。是者所以重其事也。吾年未壮则虑事不精。地不审则恐有后悔。力不足则物不备具。三者皆不可以有为也。吾所以隐忍至此者。盖有所待也。今也吾年逾弱冠。可以胜事矣。周游圻甸。以及湖中。三入镇川而后。占一隙地焉。度其面势而宜。相其阴阳而叶。质之卜筮而从。地不可谓不审矣。躬稼而节衣食。积数年而储蓄稍赢。力又可以有为矣。玆可以无待矣。然而犹不敢遽也。遍以告诸父诸舅。皆曰可。然后敢以有事。呜呼。如是而可以无憾矣。若夫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亦尽吾心之所安而已。潮汐辨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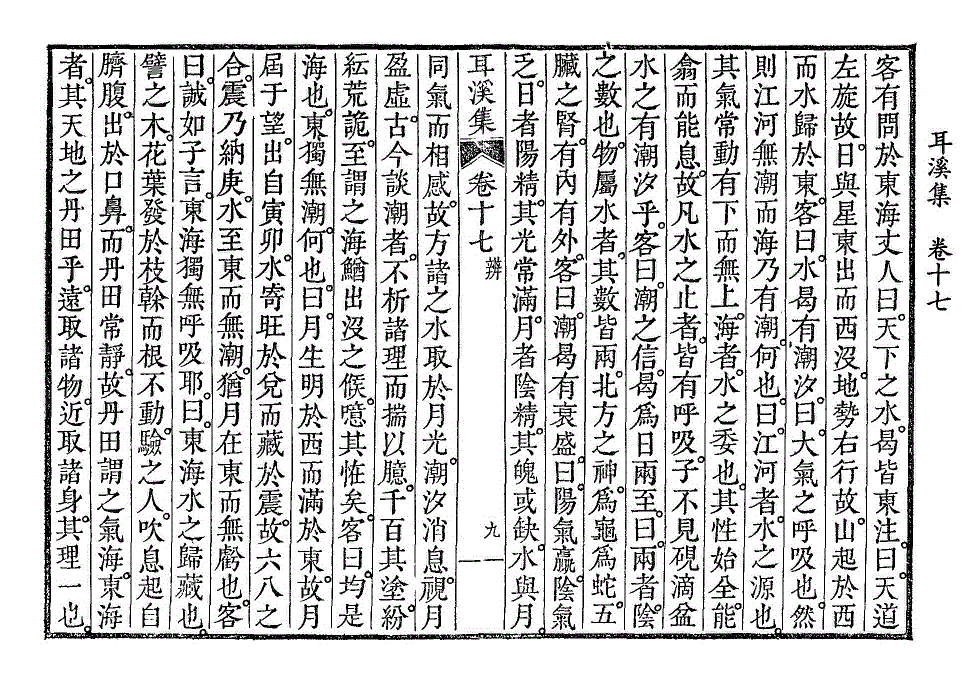 客有问于东海丈人曰。天下之水。曷皆东注。曰。天道左旋故。日与星东出而西没。地势右行故。山起于西而水归于东。客曰。水曷有潮汐。曰。大气之呼吸也。然则江河无潮而海乃有潮。何也。曰。江河者。水之源也。其气常动有下而无上。海者。水之委也。其性始全。能翕而能息。故凡水之止者。皆有呼吸。子不见砚滴盆水之有潮汐乎。客曰。潮之信。曷为日两至。曰。两者。阴之数也。物属水者。其数皆两。北方之神。为龟为蛇。五脏之肾。有内有外。客曰。潮曷有衰盛。曰。阳气赢。阴气乏。日者阳精。其光常满。月者阴精。其魄或缺。水与月。同气而相感。故方诸之水取于月光。潮汐消息。视月盈虚。古今谈潮者。不析诸理而揣以臆。千百其涂。纷纭荒诡。至谓之海䲡出没之候。噫其怪矣。客曰。均是海也。东独无潮。何也。曰。月生明于西而满于东。故月届于望。出自寅卯。水寄旺于兑而藏于震。故六八之合。震乃纳庚。水至东而无潮。犹月在东而无亏也。客曰。诚如子言。东海独无呼吸耶。曰。东海水之归藏也。譬之木。花叶发于枝干而根不动。验之人。吹息起自脐腹。出于口鼻。而丹田常静。故丹田谓之气海。东海者。其天地之丹田乎。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其理一也。
客有问于东海丈人曰。天下之水。曷皆东注。曰。天道左旋故。日与星东出而西没。地势右行故。山起于西而水归于东。客曰。水曷有潮汐。曰。大气之呼吸也。然则江河无潮而海乃有潮。何也。曰。江河者。水之源也。其气常动有下而无上。海者。水之委也。其性始全。能翕而能息。故凡水之止者。皆有呼吸。子不见砚滴盆水之有潮汐乎。客曰。潮之信。曷为日两至。曰。两者。阴之数也。物属水者。其数皆两。北方之神。为龟为蛇。五脏之肾。有内有外。客曰。潮曷有衰盛。曰。阳气赢。阴气乏。日者阳精。其光常满。月者阴精。其魄或缺。水与月。同气而相感。故方诸之水取于月光。潮汐消息。视月盈虚。古今谈潮者。不析诸理而揣以臆。千百其涂。纷纭荒诡。至谓之海䲡出没之候。噫其怪矣。客曰。均是海也。东独无潮。何也。曰。月生明于西而满于东。故月届于望。出自寅卯。水寄旺于兑而藏于震。故六八之合。震乃纳庚。水至东而无潮。犹月在东而无亏也。客曰。诚如子言。东海独无呼吸耶。曰。东海水之归藏也。譬之木。花叶发于枝干而根不动。验之人。吹息起自脐腹。出于口鼻。而丹田常静。故丹田谓之气海。东海者。其天地之丹田乎。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其理一也。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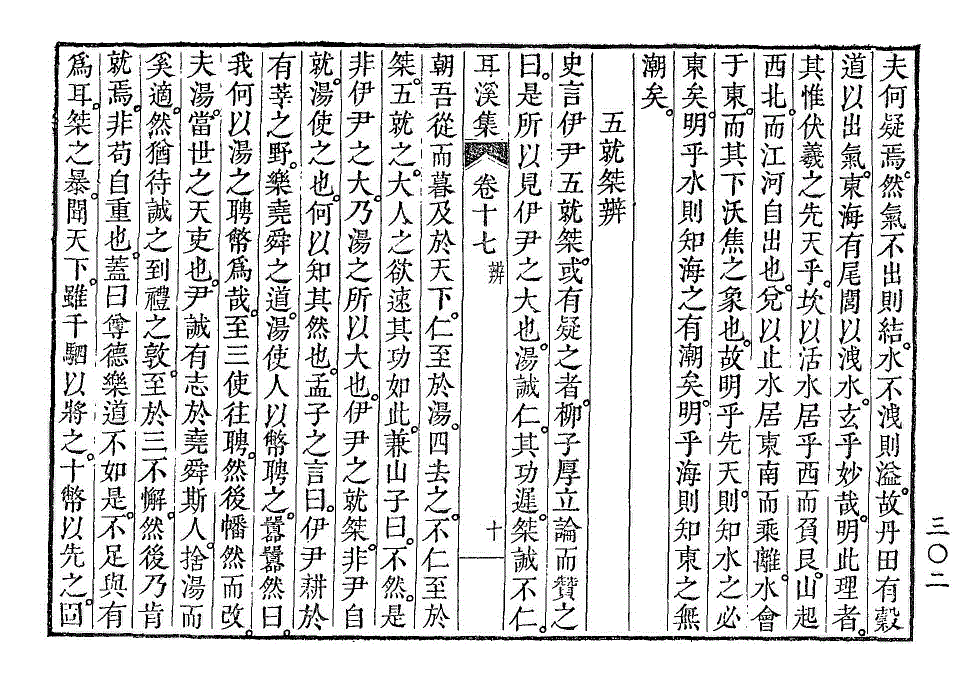 夫何疑焉。然气不出则结。水不泄则溢。故丹田有谷道以出气。东海有尾闾以泄水。玄乎妙哉。明此理者。其惟伏羲之先天乎。坎以活水居乎西而负艮。山起西北。而江河自出也。兑以止水居东南而乘离。水会于东。而其下沃焦之象也。故明乎先天。则知水之必东矣。明乎水则知海之有潮矣。明乎海则知东之无潮矣。
夫何疑焉。然气不出则结。水不泄则溢。故丹田有谷道以出气。东海有尾闾以泄水。玄乎妙哉。明此理者。其惟伏羲之先天乎。坎以活水居乎西而负艮。山起西北。而江河自出也。兑以止水居东南而乘离。水会于东。而其下沃焦之象也。故明乎先天。则知水之必东矣。明乎水则知海之有潮矣。明乎海则知东之无潮矣。五就桀辨
史言伊尹五就桀。或有疑之者。柳子厚立论而赞之曰。是所以见伊尹之大也。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仁至于汤。四去之。不仁至于桀。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兼山子曰。不然。是非伊尹之大。乃汤之所以大也。伊尹之就桀。非尹自就。汤使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孟子之言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乐尧舜之道。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至三使往聘。然后幡然而改。夫汤。当世之天吏也。尹诚有志于尧舜斯人。舍汤而奚适。然犹待诚之到礼之敦。至于三不懈。然后乃肯就焉。非苟自重也。盖曰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耳。桀之暴。闻天下。虽千驷以将之。十币以先之。固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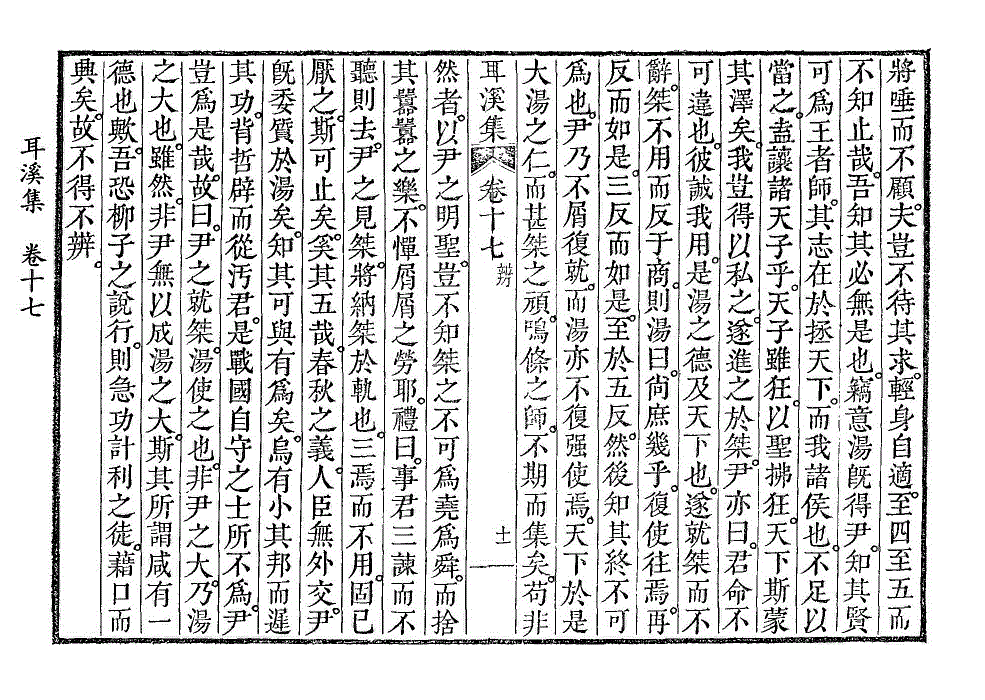 将唾而不顾。夫岂不待其求。轻身自适。至四至五而不知止哉。吾知其必无是也。窃意汤既得尹。知其贤可为王者师。其志在于拯天下。而我诸侯也。不足以当之。盍让诸天子乎。天子虽狂。以圣拂狂。天下斯蒙其泽矣。我岂得以私之。遂进之于桀。尹亦曰。君命不可违也。彼诚我用。是汤之德及天下也。遂就桀而不辞。桀不用而反于商。则汤曰。尚庶几乎。复使往焉。再反而如是。三反而如是。至于五反。然后知其终不可为也。尹乃不屑复就。而汤亦不复强使焉。天下于是大汤之仁。而甚桀之顽。鸣条之师。不期而集矣。苟非然者。以尹之明圣。岂不知桀之不可为尧为舜。而舍其嚣嚣之乐。不惮屑屑之劳耶。礼曰。事君三谏而不听则去。尹之见桀。将纳桀于轨也。三焉而不用。固已厌之。斯可止矣。奚其五哉。春秋之义。人臣无外交。尹既委质于汤矣。知其可与有为矣。乌有小其邦而迟其功。背哲辟而从污君。是战国自守之士所不为。尹岂为是哉。故曰。尹之就桀。汤使之也。非尹之大。乃汤之大也。虽然。非尹无以成汤之大。斯其所谓咸有一德也欤。吾恐柳子之说行。则急功计利之徒。藉口而兴矣。故不得不辨。
将唾而不顾。夫岂不待其求。轻身自适。至四至五而不知止哉。吾知其必无是也。窃意汤既得尹。知其贤可为王者师。其志在于拯天下。而我诸侯也。不足以当之。盍让诸天子乎。天子虽狂。以圣拂狂。天下斯蒙其泽矣。我岂得以私之。遂进之于桀。尹亦曰。君命不可违也。彼诚我用。是汤之德及天下也。遂就桀而不辞。桀不用而反于商。则汤曰。尚庶几乎。复使往焉。再反而如是。三反而如是。至于五反。然后知其终不可为也。尹乃不屑复就。而汤亦不复强使焉。天下于是大汤之仁。而甚桀之顽。鸣条之师。不期而集矣。苟非然者。以尹之明圣。岂不知桀之不可为尧为舜。而舍其嚣嚣之乐。不惮屑屑之劳耶。礼曰。事君三谏而不听则去。尹之见桀。将纳桀于轨也。三焉而不用。固已厌之。斯可止矣。奚其五哉。春秋之义。人臣无外交。尹既委质于汤矣。知其可与有为矣。乌有小其邦而迟其功。背哲辟而从污君。是战国自守之士所不为。尹岂为是哉。故曰。尹之就桀。汤使之也。非尹之大。乃汤之大也。虽然。非尹无以成汤之大。斯其所谓咸有一德也欤。吾恐柳子之说行。则急功计利之徒。藉口而兴矣。故不得不辨。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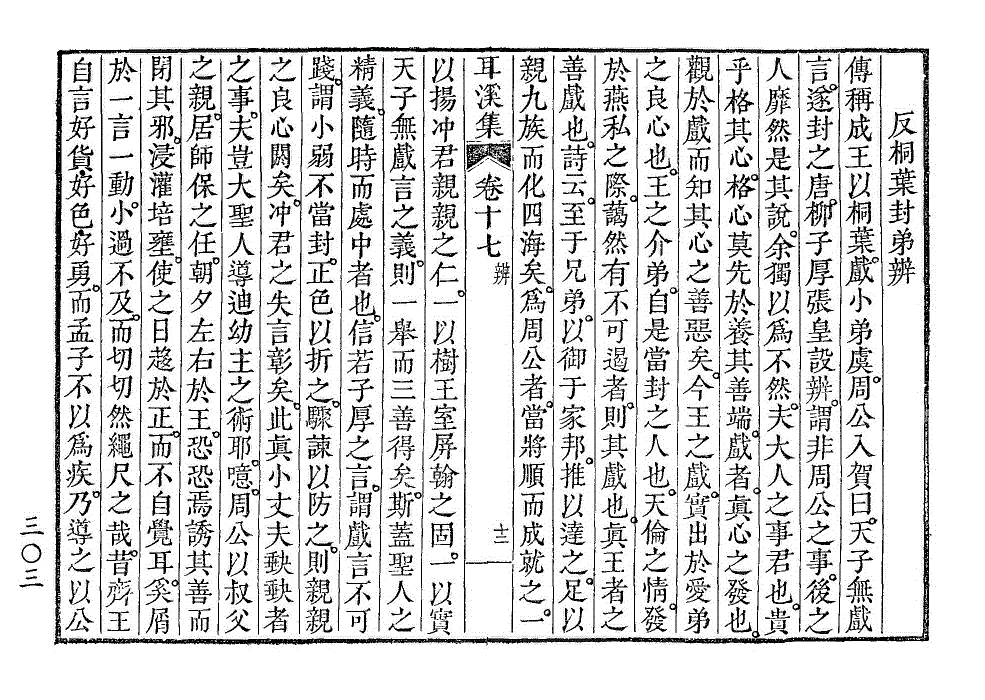 反桐叶封弟辨
反桐叶封弟辨传称成王以桐叶。戏小弟虞。周公入贺曰。天子无戏言。遂封之唐。柳子厚张皇设辨。谓非周公之事。后之人靡然是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大人之事君也。贵乎格其心。格心莫先于养其善端。戏者。真心之发也。观于戏而知其心之善恶矣。今王之戏。实出于爱弟之良心也。王之介弟。自是当封之人也。天伦之情。发于燕私之际。蔼然有不可遏者。则其戏也。真王者之善戏也。诗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推以达之。足以亲九族而化四海矣。为周公者。当将顺而成就之。一以扬冲君亲亲之仁。一以树王室屏翰之固。一以实天子无戏言之义。则一举而三善得矣。斯盖圣人之精义。随时而处中者也。信若子厚之言。谓戏言不可践。谓小弱不当封。正色以折之。骤谏以防之。则亲亲之良心阏矣。冲君之失言彰矣。此真小丈夫𡙇𡙇者之事。夫岂大圣人导迪幼主之术耶。噫。周公以叔父之亲。居师保之任。朝夕左右于王。恐恐焉诱其善而闭其邪。浸灌培壅。使之日趍于正。而不自觉耳。奚屑于一言一动。小过不及。而切切然绳尺之哉。昔齐王自言好货,好色,好勇。而孟子不以为疾。乃导之以公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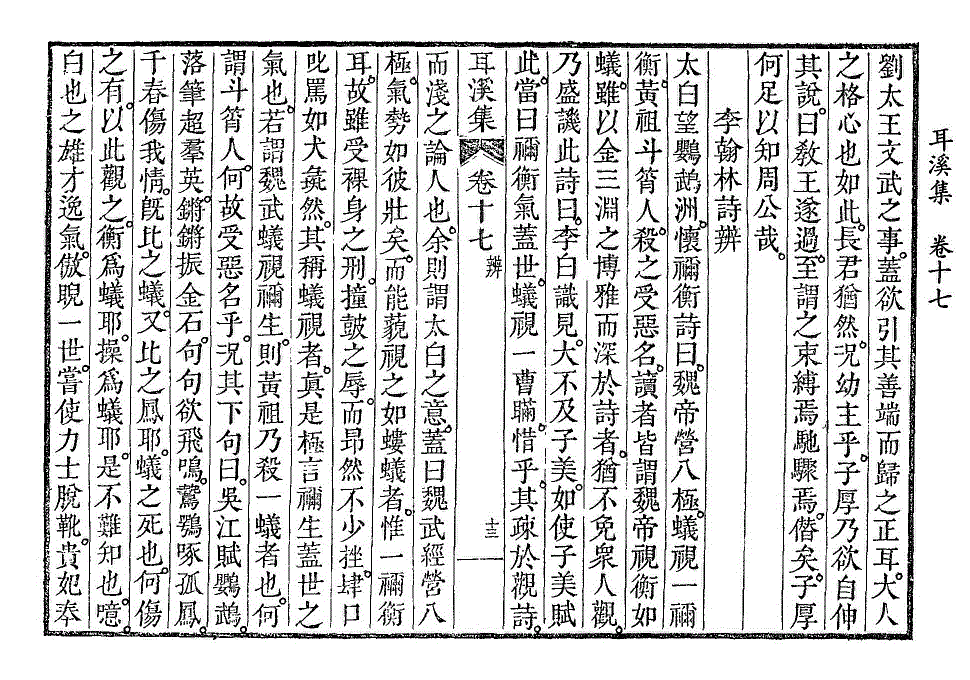 刘太王文武之事。盖欲引其善端而归之正耳。大人之格心也如此。长君犹然。况幼主乎。子厚乃欲自伸其说。曰教王遂过。至谓之束缚焉。驰骤焉。僭矣。子厚何足以知周公哉。
刘太王文武之事。盖欲引其善端而归之正耳。大人之格心也如此。长君犹然。况幼主乎。子厚乃欲自伸其说。曰教王遂过。至谓之束缚焉。驰骤焉。僭矣。子厚何足以知周公哉。李翰林诗辨
太白望鹦鹉洲。怀祢衡诗曰。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读者皆谓魏帝视衡如蚁。虽以金三渊之博雅而深于诗者。犹不免众人观。乃盛讥此诗曰。李白识见。大不及子美。如使子美赋此。当曰祢衡气盖世。蚁视一曹瞒。惜乎。其疏于观诗。而浅之论人也。余则谓太白之意。盖曰魏武经营八极。气势如彼壮矣。而能藐视之如蝼蚁者。惟一祢衡耳。故虽受裸身之刑。撞鼓之辱。而昂然不少挫。肆口叱骂如犬彘然。其称蚁视者。真是极言祢生盖世之气也。若谓魏武蚁视祢生。则黄祖乃杀一蚁者也。何谓斗筲人。何故受恶名乎。况其下句曰。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既比之蚁。又比之凤耶。蚁之死也。何伤之有。以此观之。衡为蚁耶。操为蚁耶。是不难知也。噫。白也之雄才逸气。傲睨一世。尝使力士脱靴。贵妃奉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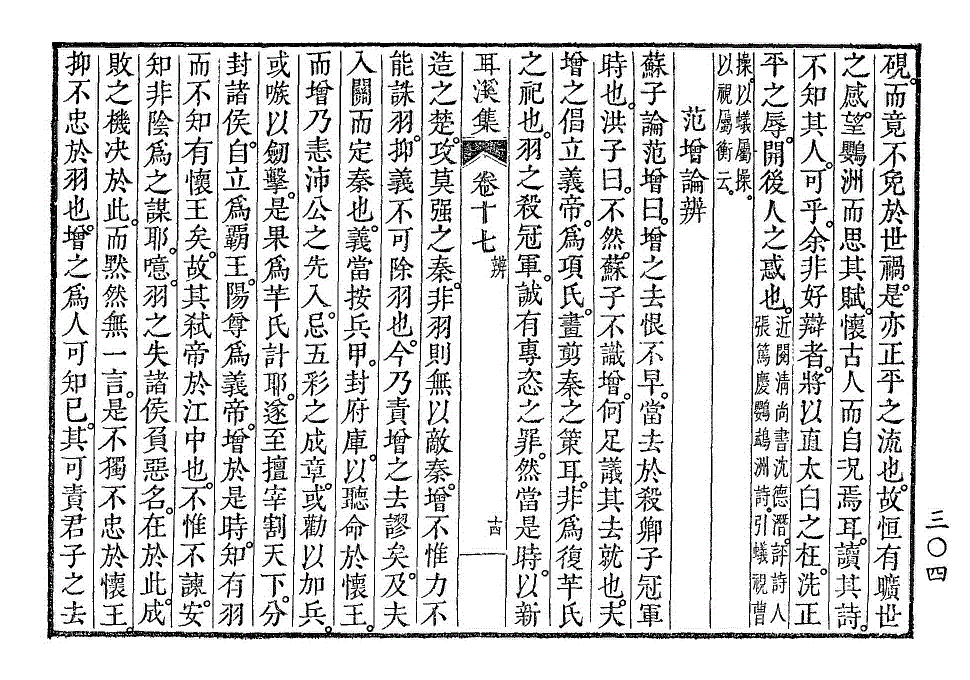 砚。而竟不免于世祸。是亦正平之流也。故恒有旷世之感。望鹦洲而思其赋。怀古人而自况焉耳。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余非好辩者。将以直太白之枉。洗正平之辱。开后人之惑也。(近阅清尚书沈德潜。评诗人张笃庆鹦鹉洲诗。引蚁视曹操。以蚁属操。以视属衡云。)
砚。而竟不免于世祸。是亦正平之流也。故恒有旷世之感。望鹦洲而思其赋。怀古人而自况焉耳。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余非好辩者。将以直太白之枉。洗正平之辱。开后人之惑也。(近阅清尚书沈德潜。评诗人张笃庆鹦鹉洲诗。引蚁视曹操。以蚁属操。以视属衡云。)范增论辨
苏子论范增曰。增之去恨不早。当去于杀卿子冠军时也。洪子曰。不然。苏子不识增。何足议其去就也。夫增之倡立义帝。为项氏。画剪秦之策耳。非为复芉(一作芈)氏之祀也。羽之杀冠军。诚有专恣之罪。然当是时。以新造之楚。攻莫强之秦。非羽则无以敌秦。增不惟力不能诛羽。抑义不可除羽也。今乃责增之去谬矣。及夫入关而定秦也。义当按兵甲。封府库。以听命于怀王。而增乃恚沛公之先入。忌五彩之成章。或劝以加兵。或嗾以剑击。是果为芉(一作芈)氏计耶。遂至擅宰割天下。分封诸侯。自立为霸王。阳尊为义帝。增于是时。知有羽而不知有怀王矣。故其弑帝于江中也。不惟不谏。安知非阴为之谋耶。噫。羽之失诸侯负恶名。在于此。成败之机决于此。而默然无一言。是不独不忠于怀王。抑不忠于羽也。增之为人可知已。其可责君子之去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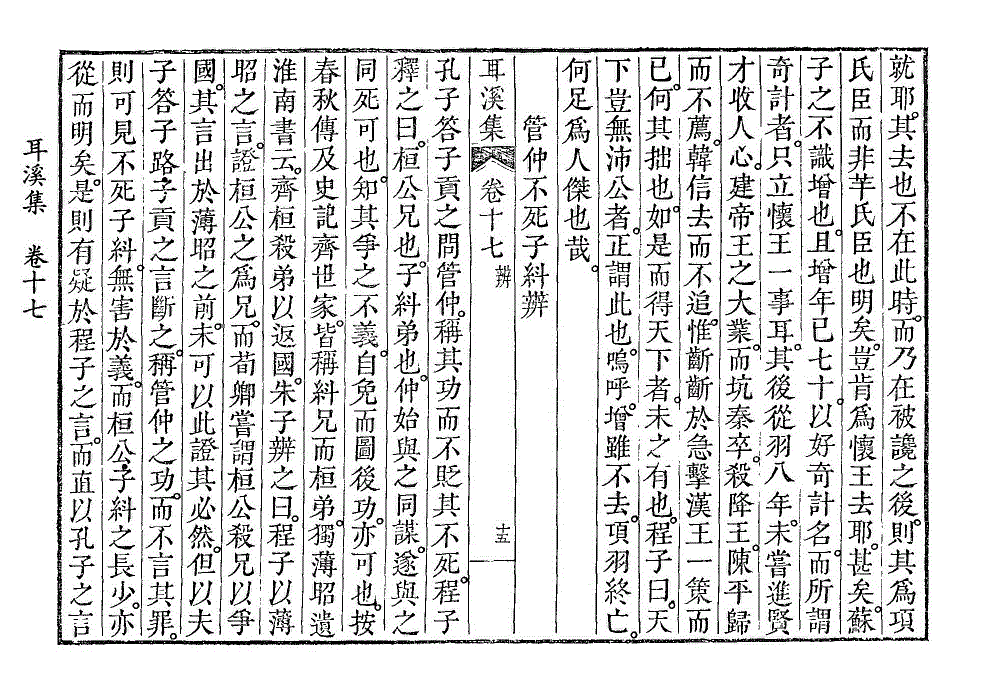 就耶。其去也不在此时。而乃在被谗之后。则其为项氏臣而非芉(一作芈)氏臣也明矣。岂肯为怀王去耶。甚矣。苏子之不识增也。且增年已七十。以好奇计名。而所谓奇计者。只立怀王一事耳。其后从羽八年。未尝进贤才收人心。建帝王之大业。而坑秦卒。杀降王。陈平归而不荐。韩信去而不追。惟龂龂于急击汉王一策而已。何其拙也。如是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岂无沛公者。正谓此也。呜呼。增虽不去。项羽终亡。何足为人杰也哉。
就耶。其去也不在此时。而乃在被谗之后。则其为项氏臣而非芉(一作芈)氏臣也明矣。岂肯为怀王去耶。甚矣。苏子之不识增也。且增年已七十。以好奇计名。而所谓奇计者。只立怀王一事耳。其后从羽八年。未尝进贤才收人心。建帝王之大业。而坑秦卒。杀降王。陈平归而不荐。韩信去而不追。惟龂龂于急击汉王一策而已。何其拙也。如是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岂无沛公者。正谓此也。呜呼。增虽不去。项羽终亡。何足为人杰也哉。管仲不死子纠辨
孔子答子贡之问管仲。称其功而不贬其不死。程子释之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其争之不义。自免而图后功。亦可也。按春秋传及史记齐世家。皆称纠兄而桓弟。独薄昭遗淮南书云。齐桓杀弟以返国。朱子辨之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为兄。而荀卿尝谓桓公杀兄以争国。其言出于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夫子答子路,子贡之言断之。称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则可见不死子纠。无害于义。而桓公,子纠之长少。亦从而明矣。是则有疑于程子之言。而直以孔子之言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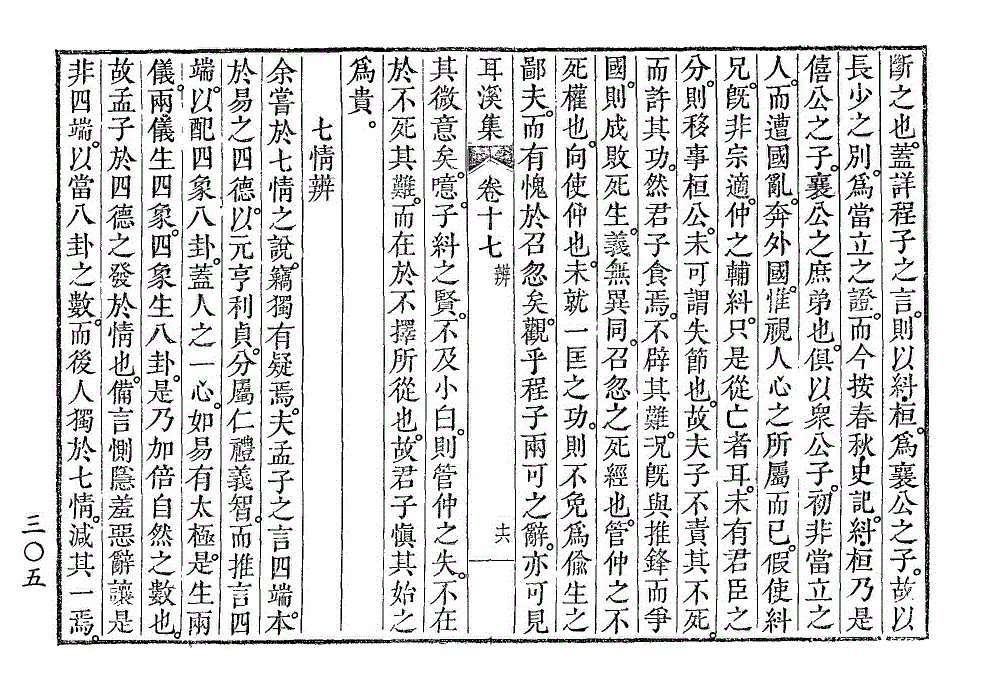 断之也。盖详程子之言。则以纠,桓。为襄公之子。故以长少之别。为当立之證。而今按春秋,史记。纠,桓乃是僖公之子。襄公之庶弟也。俱以众公子。初非当立之人。而遭国乱。奔外国。惟视人心之所属而已。假使纠兄。既非宗适。仲之辅纠。只是从亡者耳。未有君臣之分。则移事桓公。未可谓失节也。故夫子不责其不死。而许其功。然君子食焉。不辟其难。况既与推锋而争国。则成败死生。义无异同。召忽之死经也。管仲之不死权也。向使仲也。未就一匡之功。则不免为偷生之鄙夫。而有愧于召忽矣。观乎程子两可之辞。亦可见其微意矣。噫。子纠之贤。不及小白。则管仲之失。不在于不死其难。而在于不择所从也。故君子慎其始之为贵。
断之也。盖详程子之言。则以纠,桓。为襄公之子。故以长少之别。为当立之證。而今按春秋,史记。纠,桓乃是僖公之子。襄公之庶弟也。俱以众公子。初非当立之人。而遭国乱。奔外国。惟视人心之所属而已。假使纠兄。既非宗适。仲之辅纠。只是从亡者耳。未有君臣之分。则移事桓公。未可谓失节也。故夫子不责其不死。而许其功。然君子食焉。不辟其难。况既与推锋而争国。则成败死生。义无异同。召忽之死经也。管仲之不死权也。向使仲也。未就一匡之功。则不免为偷生之鄙夫。而有愧于召忽矣。观乎程子两可之辞。亦可见其微意矣。噫。子纠之贤。不及小白。则管仲之失。不在于不死其难。而在于不择所从也。故君子慎其始之为贵。七情辨
余尝于七情之说。窃独有疑焉。夫孟子之言四端。本于易之四德。以元亨利贞。分属仁礼义智。而推言四端。以配四象八卦。盖人之一心。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乃加倍自然之数也。故孟子于四德之发于情也。备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以当八卦之数。而后人独于七情。减其一焉。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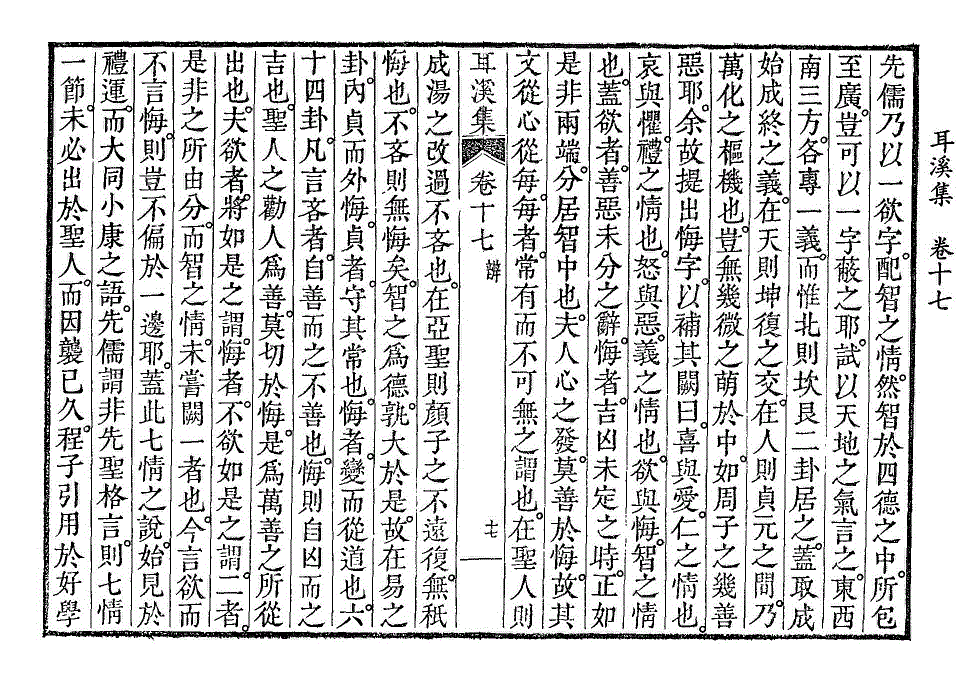 先儒乃以一欲字。配智之情。然智于四德之中。所包至广。岂可以一字蔽之耶。试以天地之气言之。东西南三方。各专一义。而惟北则坎艮二卦居之。盖取成始成终之义。在天则坤复之交。在人则贞元之间。乃万化之枢机也。岂无几微之萌于中。如周子之几善恶耶。余故提出悔字。以补其阙曰。喜与爱。仁之情也。哀与惧。礼之情也。怒与恶。义之情也。欲与悔。智之情也。盖欲者。善恶未分之辞。悔者。吉凶未定之时。正如是非两端。分居智中也。夫人心之发。莫善于悔。故其文从心从每。每者。常有而不可无之谓也。在圣人则成汤之改过不吝也。在亚圣则颜子之不远复。无秖悔也。不吝则无悔矣。智之为德。孰大于是。故在易之卦。内贞而外悔。贞者。守其常也。悔者。变而从道也。六十四卦。凡言吝者。自善而之不善也。悔则自凶而之吉也。圣人之劝人为善。莫切于悔。是为万善之所从出也。夫欲者。将如是之谓。悔者。不欲如是之谓。二者。是非之所由分。而智之情。未尝阙一者也。今言欲而不言悔。则岂不偏于一边耶。盖此七情之说。始见于礼运。而大同小康之语。先儒谓非先圣格言。则七情一节。未必出于圣人。而因袭已久。程子引用于好学
先儒乃以一欲字。配智之情。然智于四德之中。所包至广。岂可以一字蔽之耶。试以天地之气言之。东西南三方。各专一义。而惟北则坎艮二卦居之。盖取成始成终之义。在天则坤复之交。在人则贞元之间。乃万化之枢机也。岂无几微之萌于中。如周子之几善恶耶。余故提出悔字。以补其阙曰。喜与爱。仁之情也。哀与惧。礼之情也。怒与恶。义之情也。欲与悔。智之情也。盖欲者。善恶未分之辞。悔者。吉凶未定之时。正如是非两端。分居智中也。夫人心之发。莫善于悔。故其文从心从每。每者。常有而不可无之谓也。在圣人则成汤之改过不吝也。在亚圣则颜子之不远复。无秖悔也。不吝则无悔矣。智之为德。孰大于是。故在易之卦。内贞而外悔。贞者。守其常也。悔者。变而从道也。六十四卦。凡言吝者。自善而之不善也。悔则自凶而之吉也。圣人之劝人为善。莫切于悔。是为万善之所从出也。夫欲者。将如是之谓。悔者。不欲如是之谓。二者。是非之所由分。而智之情。未尝阙一者也。今言欲而不言悔。则岂不偏于一边耶。盖此七情之说。始见于礼运。而大同小康之语。先儒谓非先圣格言。则七情一节。未必出于圣人。而因袭已久。程子引用于好学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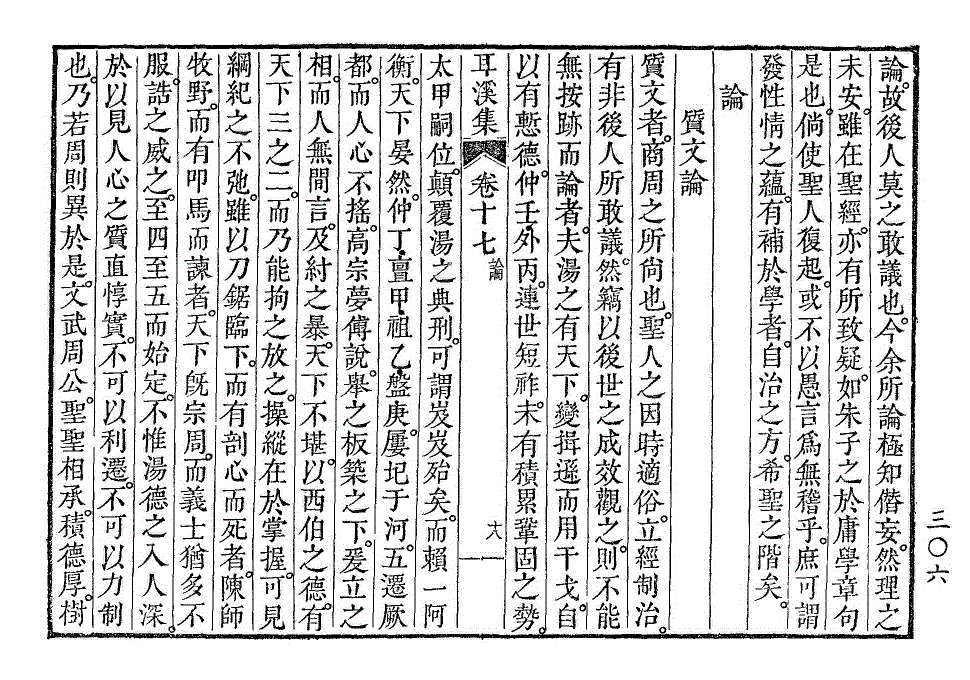 论。故后人莫之敢议也。今余所论极知僭妄。然理之未安。虽在圣经。亦有所致疑。如朱子之于庸学章句是也。倘使圣人复起。或不以愚言为无稽乎。庶可谓发性情之蕴。有补于学者。自治之方。希圣之阶矣。
论。故后人莫之敢议也。今余所论极知僭妄。然理之未安。虽在圣经。亦有所致疑。如朱子之于庸学章句是也。倘使圣人复起。或不以愚言为无稽乎。庶可谓发性情之蕴。有补于学者。自治之方。希圣之阶矣。耳溪集卷十七
论
质文论
质文者。商周之所尚也。圣人之因时适俗。立经制治。有非后人所敢议。然窃以后世之成效观之。则不能无按迹而论者。夫汤之有天下。变揖逊而用干戈。自以有惭德。仲壬,外丙。连世短祚。未有积累巩固之势。太甲嗣位。颠覆汤之典刑。可谓岌岌殆矣。而赖一阿衡。天下晏然。仲丁,亶甲,祖乙,盘庚。屡圮于河。五迁厥都。而人心不摇。高宗梦傅说。举之板筑之下。爰立之相。而人无间言。及纣之暴。天下不堪。以西伯之德。有天下三之二。而乃能拘之放之。操纵在于掌握。可见纲纪之不弛。虽以刀锯临下。而有剖心而死者。陈师牧野。而有叩马而谏者。天下既宗周。而义士犹多不服。诰之威之。至四至五而始定。不惟汤德之入人深。于以见人心之质直惇实。不可以利迁。不可以力制也。乃若周则异于是。文武周公。圣圣相承。积德厚。树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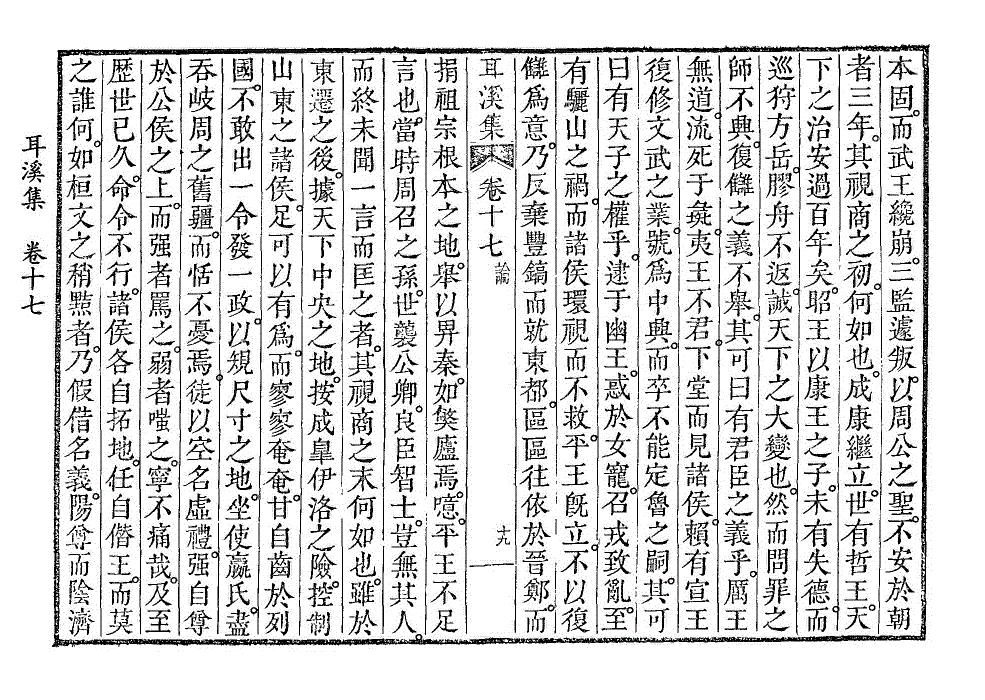 本固。而武王才崩。三监遽叛。以周公之圣。不安于朝者三年。其视商之初。何如也。成康继立。世有哲王。天下之治安过百年矣。昭王以康王之子。未有失德。而巡狩方岳。胶舟不返。诚天下之大变也。然而问罪之师不兴。复雠之义不举。其可曰有君臣之义乎。厉王无道。流死于彘。夷王不君。下堂而见诸侯。赖有宣王复修文武之业。号为中兴。而卒不能定鲁之嗣。其可曰有天子之权乎。逮于幽王。惑于女宠。召戎致乱。至有骊山之祸。而诸侯环视而不救。平王既立。不以复雠为意。乃反弃丰镐而就东都。区区往依于晋郑。而捐祖宗根本之地。举以畀秦。如弊庐焉。噫。平王不足言也。当时周召之孙。世袭公卿。良臣智士。岂无其人。而终未闻一言而匡之者。其视商之末何如也。虽于东迁之后。据天下中央之地。按成皋伊洛之险。控制山东之诸侯。足可以有为。而寥寥奄奄。甘自齿于列国。不敢出一令发一政。以规尺寸之地。坐使嬴氏。尽吞岐周之旧疆。而恬不忧焉。徒以空名虚礼。强自尊于公侯之上。而强者骂之。弱者嗤之。宁不痛哉。及至历世已久。命令不行。诸侯各自拓地。任自僭王。而莫之谁何。如桓文之稍黠者。乃假借名义。阳尊而阴济
本固。而武王才崩。三监遽叛。以周公之圣。不安于朝者三年。其视商之初。何如也。成康继立。世有哲王。天下之治安过百年矣。昭王以康王之子。未有失德。而巡狩方岳。胶舟不返。诚天下之大变也。然而问罪之师不兴。复雠之义不举。其可曰有君臣之义乎。厉王无道。流死于彘。夷王不君。下堂而见诸侯。赖有宣王复修文武之业。号为中兴。而卒不能定鲁之嗣。其可曰有天子之权乎。逮于幽王。惑于女宠。召戎致乱。至有骊山之祸。而诸侯环视而不救。平王既立。不以复雠为意。乃反弃丰镐而就东都。区区往依于晋郑。而捐祖宗根本之地。举以畀秦。如弊庐焉。噫。平王不足言也。当时周召之孙。世袭公卿。良臣智士。岂无其人。而终未闻一言而匡之者。其视商之末何如也。虽于东迁之后。据天下中央之地。按成皋伊洛之险。控制山东之诸侯。足可以有为。而寥寥奄奄。甘自齿于列国。不敢出一令发一政。以规尺寸之地。坐使嬴氏。尽吞岐周之旧疆。而恬不忧焉。徒以空名虚礼。强自尊于公侯之上。而强者骂之。弱者嗤之。宁不痛哉。及至历世已久。命令不行。诸侯各自拓地。任自僭王。而莫之谁何。如桓文之稍黠者。乃假借名义。阳尊而阴济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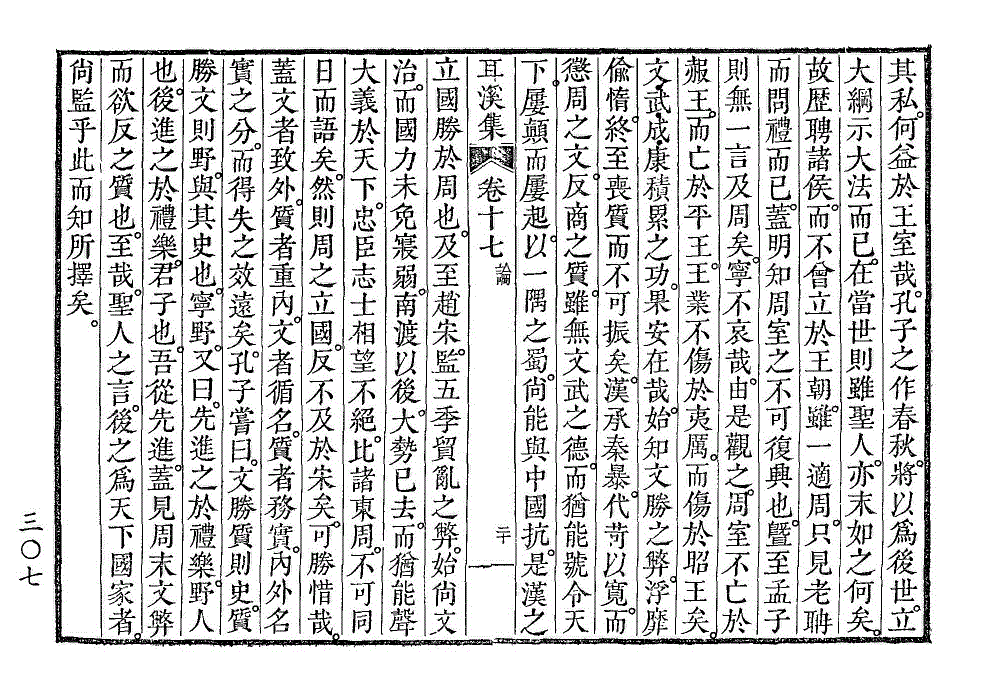 其私。何益于王室哉。孔子之作春秋。将以为后世。立大纲示大法而已。在当世则虽圣人。亦末如之何矣。故历聘诸侯。而不曾立于王朝。虽一适周。只见老聃而问礼而已。盖明知周室之不可复兴也。暨至孟子则无一言及周矣。宁不哀哉。由是观之。周室不亡于赧王。而亡于平王。王业不伤于夷厉。而伤于昭王矣。文,武,成,康积累之功。果安在哉。始知文胜之弊。浮靡偷惰。终至丧质而不可振矣。汉承秦暴。代苛以宽。而惩周之文。反商之质。虽无文武之德。而犹能号令天下。屡颠而屡起。以一隅之蜀。尚能与中国抗。是汉之立国胜于周也。及至赵宋。监五季贸乱之弊。始尚文治。而国力未免寝弱。南渡以后。大势已去。而犹能声大义于天下。忠臣志士相望不绝。比诸东周。不可同日而语矣。然则周之立国。反不及于宋矣。可胜惜哉。盖文者致外。质者重内。文者循名。质者务实。内外名实之分。而得失之效远矣。孔子尝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与其史也。宁野。又曰。先进之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之于礼乐。君子也。吾从先进。盖见周末文弊而欲反之质也。至哉。圣人之言。后之为天下国家者。尚监乎此而知所择矣。
其私。何益于王室哉。孔子之作春秋。将以为后世。立大纲示大法而已。在当世则虽圣人。亦末如之何矣。故历聘诸侯。而不曾立于王朝。虽一适周。只见老聃而问礼而已。盖明知周室之不可复兴也。暨至孟子则无一言及周矣。宁不哀哉。由是观之。周室不亡于赧王。而亡于平王。王业不伤于夷厉。而伤于昭王矣。文,武,成,康积累之功。果安在哉。始知文胜之弊。浮靡偷惰。终至丧质而不可振矣。汉承秦暴。代苛以宽。而惩周之文。反商之质。虽无文武之德。而犹能号令天下。屡颠而屡起。以一隅之蜀。尚能与中国抗。是汉之立国胜于周也。及至赵宋。监五季贸乱之弊。始尚文治。而国力未免寝弱。南渡以后。大势已去。而犹能声大义于天下。忠臣志士相望不绝。比诸东周。不可同日而语矣。然则周之立国。反不及于宋矣。可胜惜哉。盖文者致外。质者重内。文者循名。质者务实。内外名实之分。而得失之效远矣。孔子尝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与其史也。宁野。又曰。先进之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之于礼乐。君子也。吾从先进。盖见周末文弊而欲反之质也。至哉。圣人之言。后之为天下国家者。尚监乎此而知所择矣。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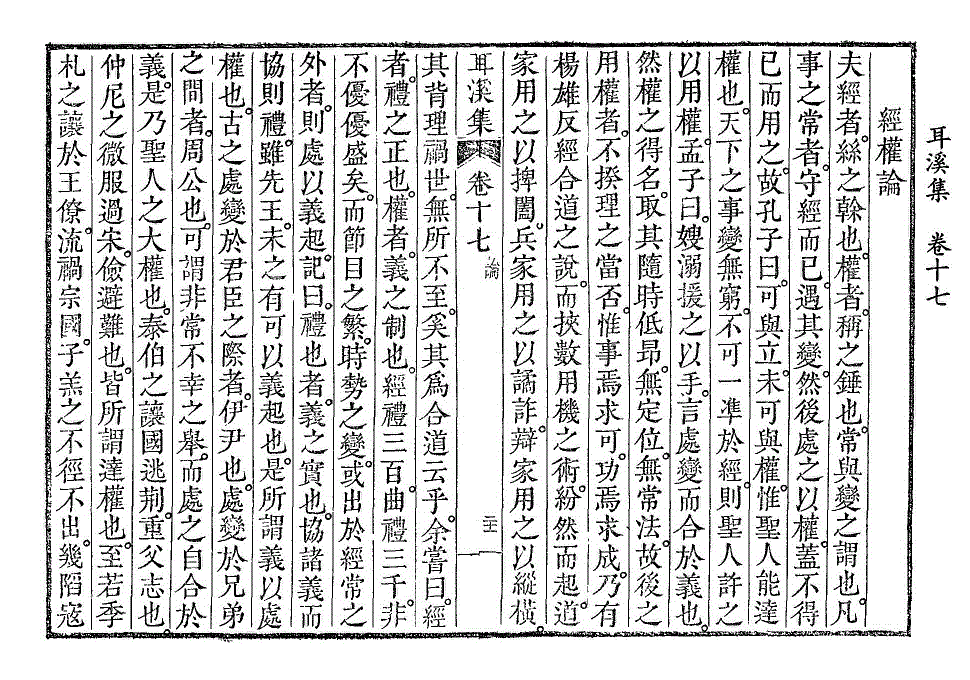 经权论
经权论夫经者。丝之干也。权者。称之锤也。常与变之谓也。凡事之常者。守经而已。遇其变。然后处之以权。盖不得已而用之。故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惟圣人能达权也。天下之事变无穷。不可一准于经。则圣人许之以用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言处变而合于义也。然权之得名。取其随时低昂。无定位。无常法。故后之用权者。不揆理之当否。惟事焉求可。功焉求成。乃有杨雄反经合道之说。而挟数用机之术。纷然而起。道家用之以捭阖。兵家用之以谲诈。辩家用之以纵横。其背理祸世。无所不至。奚其为合道云乎。余尝曰。经者。礼之正也。权者。义之制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非不优优盛矣。而节目之繁。时势之变。或出于经常之外者。则处以义起。记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是所谓义以处权也。古之处变于君臣之际者。伊尹也。处变于兄弟之间者。周公也。可谓非常不幸之举。而处之自合于义。是乃圣人之大权也。泰伯之让国逃荆。重父志也。仲尼之微服过宋。俭避难也。皆所谓达权也。至若季札之让于王僚。流祸宗国。子羔之不径不出。几陷寇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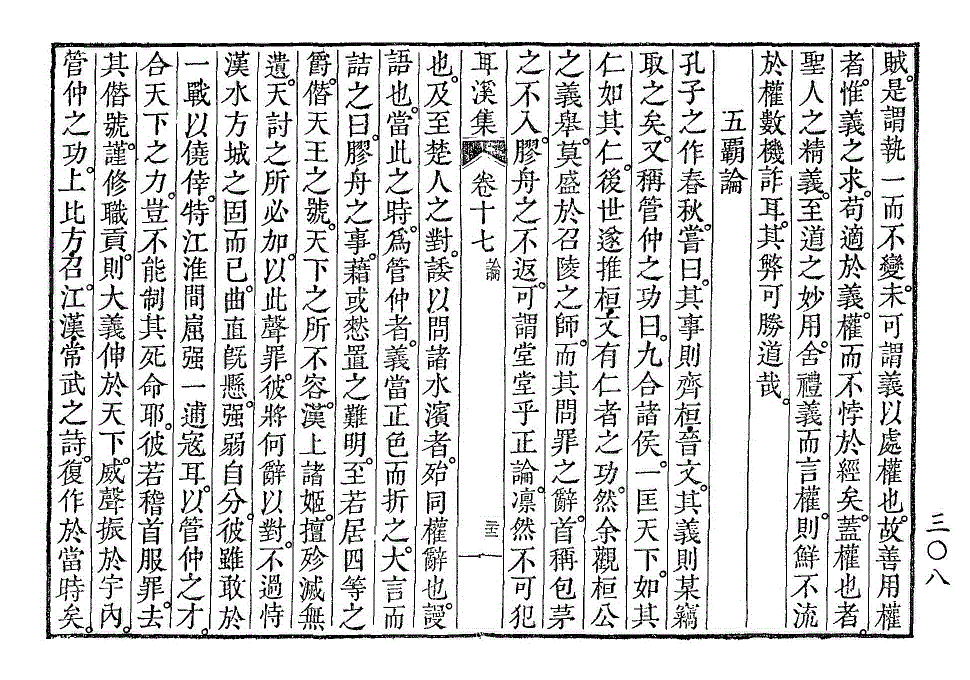 贼。是谓执一而不变。未可谓义以处权也。故善用权者。惟义之求。苟适于义。权而不悖于经矣。盖权也者。圣人之精义。至道之妙用。舍礼义而言权。则鲜不流于权数机诈耳。其弊可胜道哉。
贼。是谓执一而不变。未可谓义以处权也。故善用权者。惟义之求。苟适于义。权而不悖于经矣。盖权也者。圣人之精义。至道之妙用。舍礼义而言权。则鲜不流于权数机诈耳。其弊可胜道哉。五霸论
孔子之作春秋。尝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又称管仲之功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其仁如其仁。后世遂推桓,文有仁者之功。然余观桓公之义举。莫盛于召陵之师。而其问罪之辞。首称包茅之不入。胶舟之不返。可谓堂堂乎正论。凛然不可犯也。及至楚人之对。诿以问诸水滨者。殆同权辞也。谩语也。当此之时。为管仲者。义当正色而折之。大言而诘之曰。胶舟之事。藉或憖置之难明。至若居四等之爵。僭天王之号。天下之所不容。汉上诸姬。擅殄灭无遗。天讨之所必加。以此声罪。彼将何辞以对。不过恃汉水方城之固而已。曲直既悬。强弱自分。彼虽敢于一战以侥倖。特江淮间崛强一逋寇耳。以管仲之才。合天下之力。岂不能制其死命耶。彼若稽首服罪。去其僭号。谨修职贡。则大义伸于天下。威声振于宇内。管仲之功。上比方,召。江汉,常武之诗。复作于当时矣。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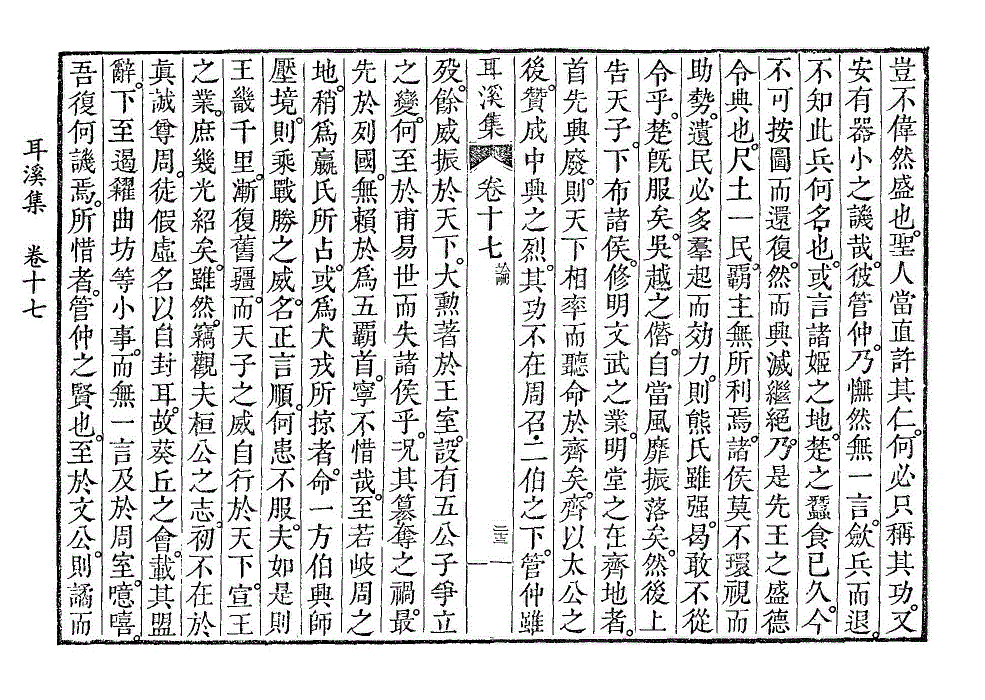 岂不伟然盛也。圣人当直许其仁。何必只称其功。又安有器小之讥哉。彼管仲。乃怃然无一言。敛兵而退。不知此兵何名也。或言诸姬之地。楚之蚕食已久。今不可按图而还复。然而兴灭继绝。乃是先王之盛德令典也。尺土一民。霸主无所利焉。诸侯莫不环视而助势。遗民必多群起而效力。则熊氏虽强。曷敢不从令乎。楚既服矣。吴越之僭。自当风靡振落矣。然后上告天子。下布诸侯。修明文武之业。明堂之在齐地者。首先兴废。则天下相率而听命于齐矣。齐以太公之后。赞成中兴之烈。其功不在周召,二伯之下。管仲虽殁。馀威振于天下。大勋著于王室。设有五公子争立之变。何至于甫易世而失诸侯乎。况其篡夺之祸。最先于列国。无赖于为五霸首。宁不惜哉。至若岐周之地。稍为嬴氏所占。或为犬戎所掠者。命一方伯兴师压境。则乘战胜之威。名正言顺。何患不服。夫如是则王畿千里。渐复旧疆。而天子之威自行于天下。宣王之业。庶几光绍矣。虽然。窃观夫桓公之志。初不在于真诚尊周。徒假虚名以自封耳。故葵丘之会。载其盟辞。下至遏籴曲坊等小事。而无一言及于周室。噫嘻。吾复何讥焉。所惜者。管仲之贤也。至于文公。则谲而
岂不伟然盛也。圣人当直许其仁。何必只称其功。又安有器小之讥哉。彼管仲。乃怃然无一言。敛兵而退。不知此兵何名也。或言诸姬之地。楚之蚕食已久。今不可按图而还复。然而兴灭继绝。乃是先王之盛德令典也。尺土一民。霸主无所利焉。诸侯莫不环视而助势。遗民必多群起而效力。则熊氏虽强。曷敢不从令乎。楚既服矣。吴越之僭。自当风靡振落矣。然后上告天子。下布诸侯。修明文武之业。明堂之在齐地者。首先兴废。则天下相率而听命于齐矣。齐以太公之后。赞成中兴之烈。其功不在周召,二伯之下。管仲虽殁。馀威振于天下。大勋著于王室。设有五公子争立之变。何至于甫易世而失诸侯乎。况其篡夺之祸。最先于列国。无赖于为五霸首。宁不惜哉。至若岐周之地。稍为嬴氏所占。或为犬戎所掠者。命一方伯兴师压境。则乘战胜之威。名正言顺。何患不服。夫如是则王畿千里。渐复旧疆。而天子之威自行于天下。宣王之业。庶几光绍矣。虽然。窃观夫桓公之志。初不在于真诚尊周。徒假虚名以自封耳。故葵丘之会。载其盟辞。下至遏籴曲坊等小事。而无一言及于周室。噫嘻。吾复何讥焉。所惜者。管仲之贤也。至于文公。则谲而耳溪集卷十七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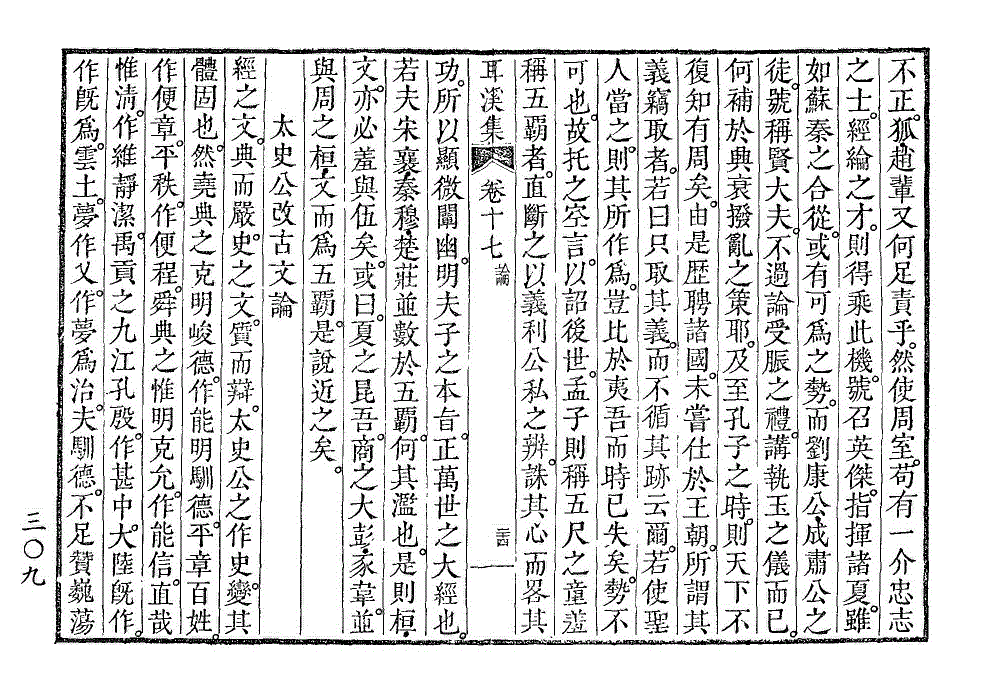 不正。狐,赵辈又何足责乎。然使周室。苟有一介忠志之士。经纶之才。则得乘此机。号召英杰。指挥诸夏。虽如苏秦之合从。或有可为之势。而刘康公,成肃公之徒。号称贤大夫。不过论受脤之礼。讲执玉之仪而已。何补于兴衰拨乱之策耶。及至孔子之时。则天下不复知有周矣。由是历聘诸国。未当仕于王朝。所谓其义窃取者。若曰只取其义。而不循其迹云尔。若使圣人当之。则其所作为。岂比于夷吾而时已失矣。势不可也。故托之空言。以诏后世。孟子则称五尺之童羞称五霸者。直断之以义利公私之辨。诛其心而略其功。所以显微阐幽。明夫子之本旨。正万世之大经也。若夫宋襄,秦穆,楚庄并数于五霸。何其滥也。是则桓,文。亦必羞与伍矣。或曰。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韦。并与周之桓,文而为五霸。是说近之矣。
不正。狐,赵辈又何足责乎。然使周室。苟有一介忠志之士。经纶之才。则得乘此机。号召英杰。指挥诸夏。虽如苏秦之合从。或有可为之势。而刘康公,成肃公之徒。号称贤大夫。不过论受脤之礼。讲执玉之仪而已。何补于兴衰拨乱之策耶。及至孔子之时。则天下不复知有周矣。由是历聘诸国。未当仕于王朝。所谓其义窃取者。若曰只取其义。而不循其迹云尔。若使圣人当之。则其所作为。岂比于夷吾而时已失矣。势不可也。故托之空言。以诏后世。孟子则称五尺之童羞称五霸者。直断之以义利公私之辨。诛其心而略其功。所以显微阐幽。明夫子之本旨。正万世之大经也。若夫宋襄,秦穆,楚庄并数于五霸。何其滥也。是则桓,文。亦必羞与伍矣。或曰。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韦。并与周之桓,文而为五霸。是说近之矣。太史公改古文论
经之文。典而严。史之文。质而辩。太史公之作史。变其体固也。然尧典之克明峻德。作能明驯德。平章百姓。作便章。平秩。作便程。舜典之惟明克允。作能信。直哉惟清。作维静洁。禹贡之九江孔殷。作甚中。大陆既作。作既为。云土。梦作乂。作梦为治。夫驯德。不足赞巍荡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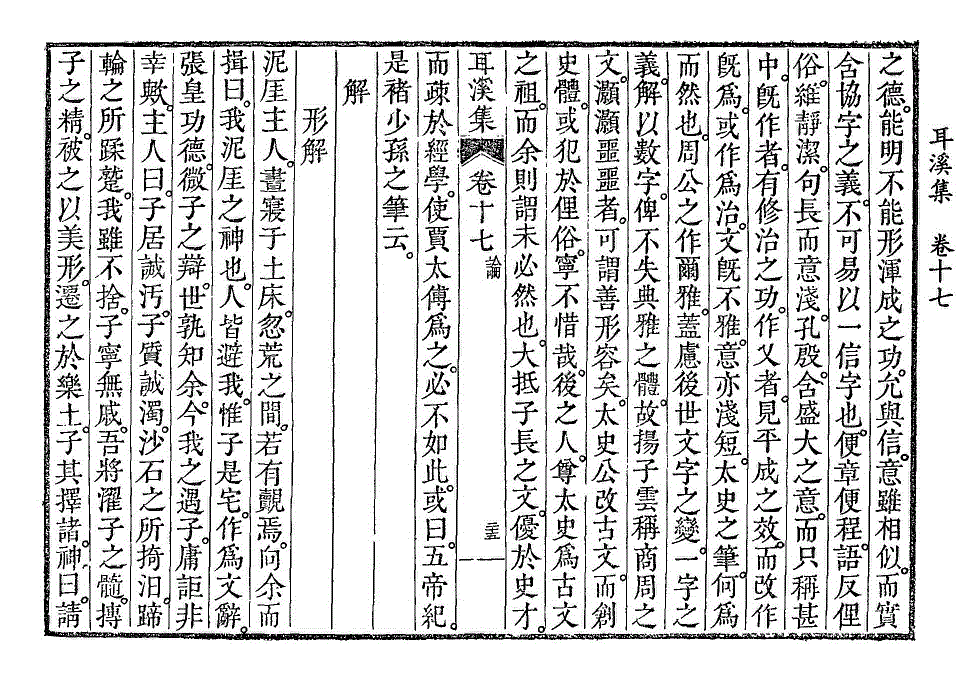 之德。能明不能形浑成之功。允与信。意虽相似。而实含协字之义。不可易以一信字也。便章便程。语反俚俗。维静洁。句长而意浅。孔殷。含盛大之意。而只称甚中。既作者。有修治之功。作乂者。见平成之效。而改作既为。或作为治。文既不雅。意亦浅短。太史之笔。何为而然也。周公之作尔雅。盖虑后世文字之变。一字之义。解以数字。俾不失典雅之体。故扬子云称商周之文。灏灏噩噩者。可谓善形容矣。太史公改古文。而创史体。或犯于俚俗。宁不惜哉。后之人。尊太史为古文之祖。而余则谓未必然也。大抵子长之文。优于史才。而疏于经学。使贾太傅为之。必不如此。或曰。五帝纪。是褚少孙之笔云。
之德。能明不能形浑成之功。允与信。意虽相似。而实含协字之义。不可易以一信字也。便章便程。语反俚俗。维静洁。句长而意浅。孔殷。含盛大之意。而只称甚中。既作者。有修治之功。作乂者。见平成之效。而改作既为。或作为治。文既不雅。意亦浅短。太史之笔。何为而然也。周公之作尔雅。盖虑后世文字之变。一字之义。解以数字。俾不失典雅之体。故扬子云称商周之文。灏灏噩噩者。可谓善形容矣。太史公改古文。而创史体。或犯于俚俗。宁不惜哉。后之人。尊太史为古文之祖。而余则谓未必然也。大抵子长之文。优于史才。而疏于经学。使贾太傅为之。必不如此。或曰。五帝纪。是褚少孙之笔云。耳溪集卷十七
解
形解
泥厓主人。昼寝于土床。忽荒之间。若有觌焉。向余而揖曰。我泥厓之神也。人皆避我。惟子是宅。作为文辞。张皇功德。微子之辩。世孰知余。今我之遇子。庸讵非幸欤。主人曰。子居诚污。子质诚浊。沙石之所掎汨。蹄轮之所蹂蹴。我虽不舍。子宁无戚。吾将濯子之髓。抟子之精。被之以美形。迁之于乐土。子其择诸。神曰。请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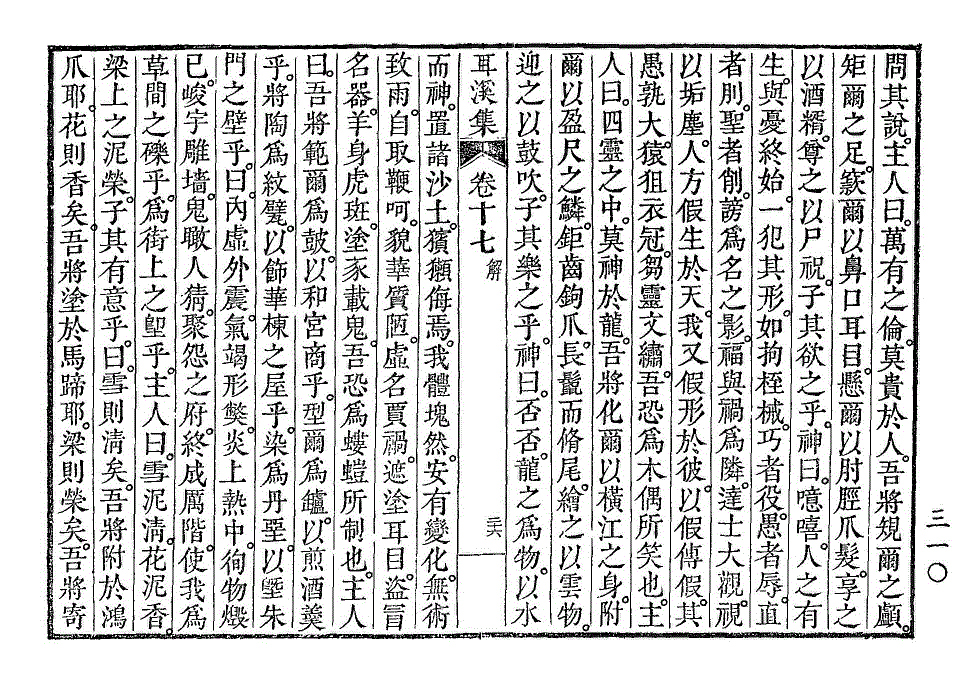 问其说。主人曰。万有之伦。莫贵于人。吾将规尔之颅。矩尔之足。窾尔以鼻口耳目。悬尔以肘胫爪发。享之以酒糈。尊之以尸祝。子其欲之乎。神曰。噫嘻。人之有生。与忧终始。一犯其形。如拘桎械。巧者役。愚者辱。直者刖。圣者削。谤为名之影。福与祸为邻。达士大观。视以垢尘。人方假生于天。我又假形于彼。以假传假。其愚孰大。猿狙衣冠。刍灵文绣。吾恐为木偶所笑也。主人曰。四灵之中。莫神于龙。吾将化尔以横江之身。附尔以盈尺之鳞。钜齿钩爪。长鬣而脩尾。绘之以云物。迎之以鼓吹。子其乐之乎。神曰。否否。龙之为物。以水而神。置诸沙土。猵獭侮焉。我体块然。安有变化。无术致雨。自取鞭呵。貌华质陋。虚名贾祸。遮涂耳目。盗冒名器。羊身虎斑。涂豕载鬼。吾恐为蝼蚁所制也。主人曰。吾将范尔为鼓。以和宫商乎。型尔为垆。以煎酒羹乎。将陶为纹甓。以饰华栋之屋乎。染为丹垩。以塈朱门之壁乎。曰。内虚外震。气竭形弊。炎上热中。徇物燬已。峻宇雕墙。鬼瞰人猜。聚怨之府。终成厉阶。使我为草间之砾乎。为街上之堲乎。主人曰。雪泥清。花泥香。梁上之泥荣。子其有意乎。曰。雪则清矣。吾将附于鸿爪耶。花则香矣。吾将涂于马蹄耶。梁则荣矣。吾将寄
问其说。主人曰。万有之伦。莫贵于人。吾将规尔之颅。矩尔之足。窾尔以鼻口耳目。悬尔以肘胫爪发。享之以酒糈。尊之以尸祝。子其欲之乎。神曰。噫嘻。人之有生。与忧终始。一犯其形。如拘桎械。巧者役。愚者辱。直者刖。圣者削。谤为名之影。福与祸为邻。达士大观。视以垢尘。人方假生于天。我又假形于彼。以假传假。其愚孰大。猿狙衣冠。刍灵文绣。吾恐为木偶所笑也。主人曰。四灵之中。莫神于龙。吾将化尔以横江之身。附尔以盈尺之鳞。钜齿钩爪。长鬣而脩尾。绘之以云物。迎之以鼓吹。子其乐之乎。神曰。否否。龙之为物。以水而神。置诸沙土。猵獭侮焉。我体块然。安有变化。无术致雨。自取鞭呵。貌华质陋。虚名贾祸。遮涂耳目。盗冒名器。羊身虎斑。涂豕载鬼。吾恐为蝼蚁所制也。主人曰。吾将范尔为鼓。以和宫商乎。型尔为垆。以煎酒羹乎。将陶为纹甓。以饰华栋之屋乎。染为丹垩。以塈朱门之壁乎。曰。内虚外震。气竭形弊。炎上热中。徇物燬已。峻宇雕墙。鬼瞰人猜。聚怨之府。终成厉阶。使我为草间之砾乎。为街上之堲乎。主人曰。雪泥清。花泥香。梁上之泥荣。子其有意乎。曰。雪则清矣。吾将附于鸿爪耶。花则香矣。吾将涂于马蹄耶。梁则荣矣。吾将寄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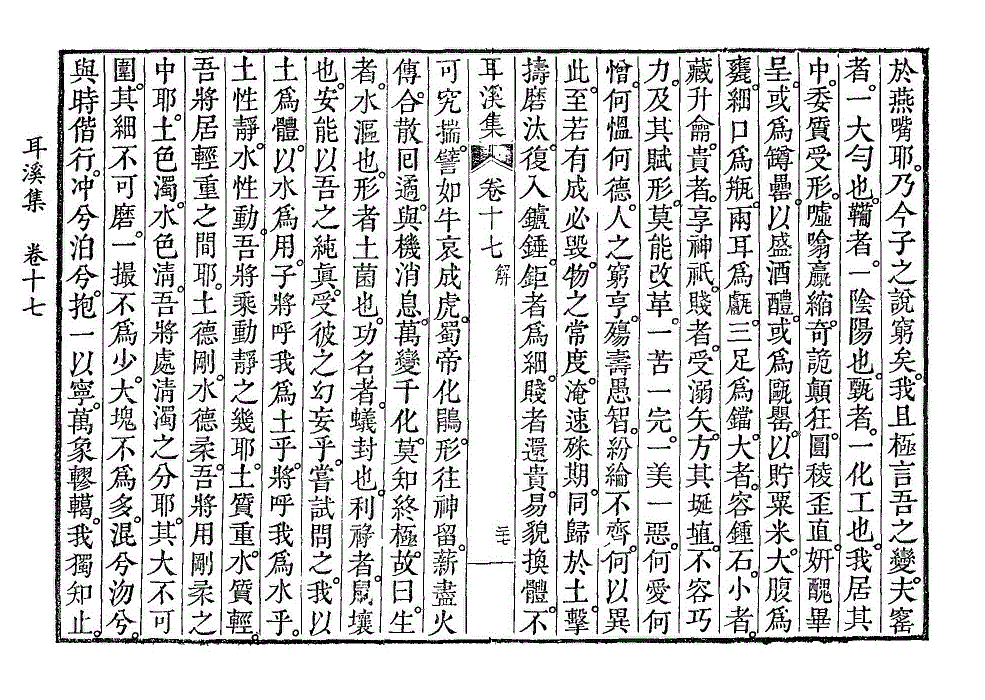 于燕嘴耶。乃今子之说穷矣。我且极言吾之变。夫窑者。一大匀也。鞴者。一阴阳也。甄者。一化工也。我居其中。委质受形。嘘噏赢缩。奇诡颠狂。圆棱歪直。妍丑毕呈。或为樽罍。以盛酒醴。或为瓯罂。以贮粟米。大腹为瓮。细口为瓶。两耳为甗。三足为铛。大者。容钟石。小者。藏升龠。贵者。享神祇。贱者。受溺矢。方其埏埴。不容巧力。及其赋形。莫能改革。一苦一完。一美一恶。何爱何憎。何愠何德。人之穷亨。殇寿愚智。纷纶不齐。何以异此。至若有成必毁。物之常度。淹速殊期。同归于土。击捣磨汰。复入炉锤。钜者为细。贱者还贵。易貌换体。不可究揣。譬如牛哀成虎。蜀帝化鹃。形往神留。薪尽火传。合散回遹。与机消息。万变千化。莫知终极。故曰。生者。水沤也。形者土菌也。功名者。蚁封也。利禄者。鼠壤也。安能以吾之纯真。受彼之幻妄乎。尝试问之。我以土为体。以水为用。子将呼我为土乎。将呼我为水乎。土性静。水性动。吾将乘动静之几耶。土质重。水质轻。吾将居轻重之间耶。土德刚。水德柔。吾将用刚柔之中耶。土色浊。水色清。吾将处清浊之分耶。其大不可围。其细不可磨。一撮不为少。大块不为多。混兮沕兮。与时偕行。冲兮泊兮。抱一以宁。万象轇轕。我独知止。
于燕嘴耶。乃今子之说穷矣。我且极言吾之变。夫窑者。一大匀也。鞴者。一阴阳也。甄者。一化工也。我居其中。委质受形。嘘噏赢缩。奇诡颠狂。圆棱歪直。妍丑毕呈。或为樽罍。以盛酒醴。或为瓯罂。以贮粟米。大腹为瓮。细口为瓶。两耳为甗。三足为铛。大者。容钟石。小者。藏升龠。贵者。享神祇。贱者。受溺矢。方其埏埴。不容巧力。及其赋形。莫能改革。一苦一完。一美一恶。何爱何憎。何愠何德。人之穷亨。殇寿愚智。纷纶不齐。何以异此。至若有成必毁。物之常度。淹速殊期。同归于土。击捣磨汰。复入炉锤。钜者为细。贱者还贵。易貌换体。不可究揣。譬如牛哀成虎。蜀帝化鹃。形往神留。薪尽火传。合散回遹。与机消息。万变千化。莫知终极。故曰。生者。水沤也。形者土菌也。功名者。蚁封也。利禄者。鼠壤也。安能以吾之纯真。受彼之幻妄乎。尝试问之。我以土为体。以水为用。子将呼我为土乎。将呼我为水乎。土性静。水性动。吾将乘动静之几耶。土质重。水质轻。吾将居轻重之间耶。土德刚。水德柔。吾将用刚柔之中耶。土色浊。水色清。吾将处清浊之分耶。其大不可围。其细不可磨。一撮不为少。大块不为多。混兮沕兮。与时偕行。冲兮泊兮。抱一以宁。万象轇轕。我独知止。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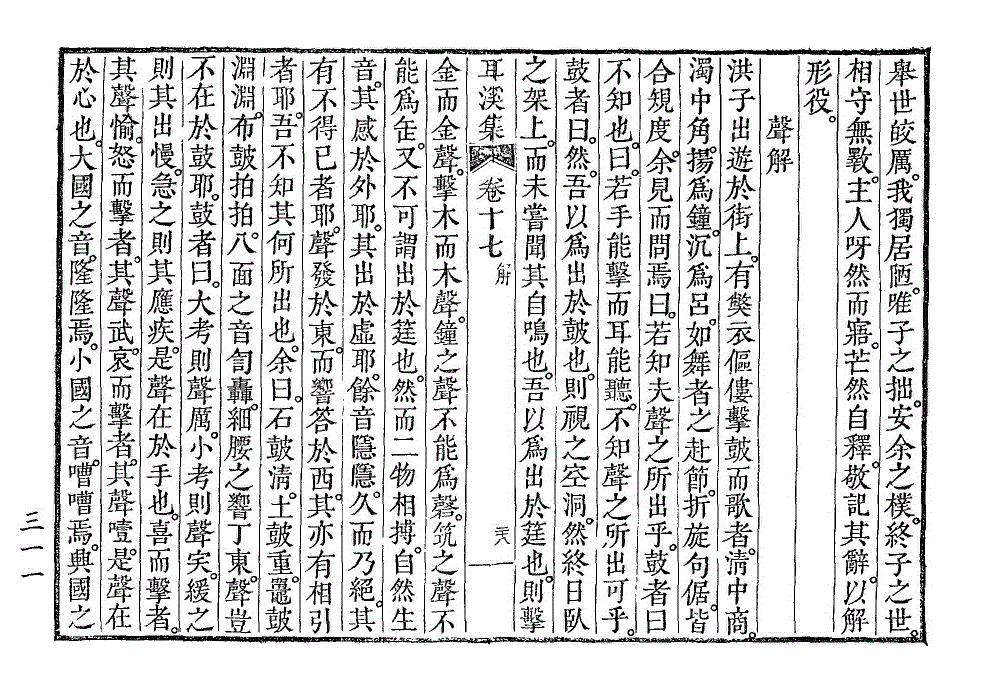 举世皎厉。我独居陋。唯子之拙。安余之朴。终子之世。相守无斁。主人呀然而寤。芒然自释。敬记其辞。以解形役。
举世皎厉。我独居陋。唯子之拙。安余之朴。终子之世。相守无斁。主人呀然而寤。芒然自释。敬记其辞。以解形役。声解
洪子出游于街上。有弊衣伛偻击鼓而歌者。清中商。浊中角。扬为钟。沉为吕。如舞者之赴节。折旋句倨。皆合规度。余见而问焉曰。若知夫声之所出乎。鼓者曰。不知也。曰。若手能击而耳能听。不知声之所出可乎。鼓者曰。然。吾以为出于鼓也。则视之空洞。然终日卧之架上。而未尝闻其自鸣也。吾以为出于筳也。则击金而金声。击木而木声。钟之声不能为磬。筑之声不能为缶。又不可谓出于筳也。然而二物相搏。自然生音。其感于外耶。其出于虚耶。馀音隐隐。久而乃绝。其有不得已者耶。声发于东。而响答于西。其亦有相引者耶。吾不知其何所出也。余曰。石鼓清。土鼓重。鼍鼓渊渊。布鼓拍拍。八面之音訇轰。细腰之响丁东。声岂不在于鼓耶。鼓者曰。大考则声厉。小考则声宎。缓之则其出慢。急之则其应疾。是声在于手也。喜而击者。其声愉。怒而击者。其声武。哀而击者。其声噎。是声在于心也。大国之音。隆隆焉。小国之音。嘈嘈焉。兴国之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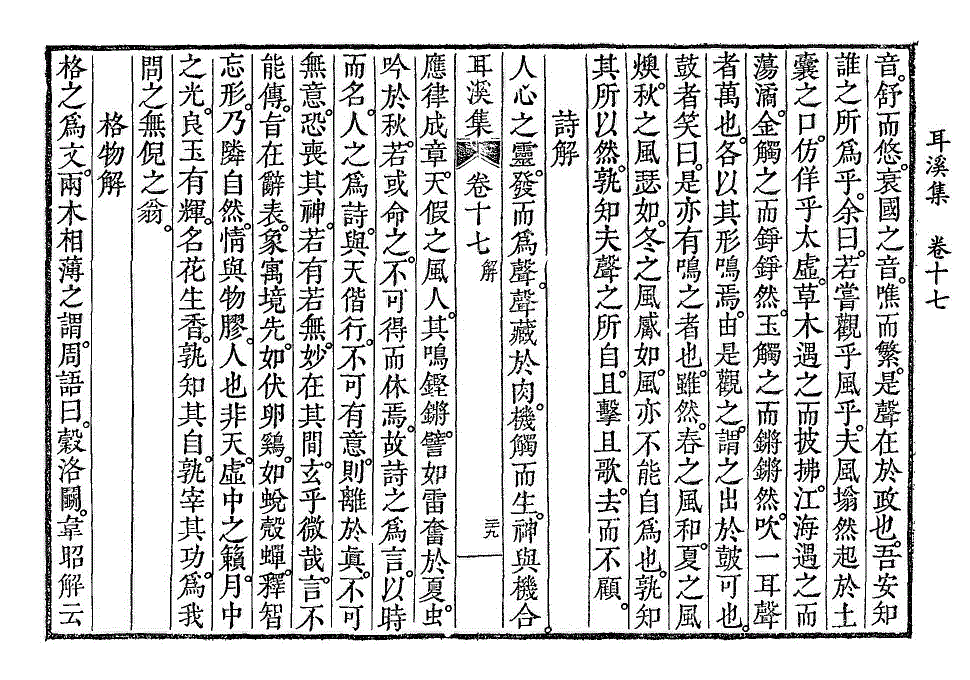 音。舒而悠。衰国之音。噍而繁。是声在于政也。吾安知谁之所为乎。余曰。若尝观乎风乎。夫风塕然起于土囊之口。仿佯乎太虚。草木遇之而披拂。江海遇之而荡潏。金触之而铮铮然。玉触之而锵锵然。吹一耳声者万也。各以其形鸣焉。由是观之。谓之出于鼓可也。鼓者笑曰。是亦有鸣之者也。虽然。春之风和。夏之风燠。秋之风瑟如。冬之风觱如。风亦不能自为也。孰知其所以然。孰知夫声之所自。且击且歌。去而不顾。
音。舒而悠。衰国之音。噍而繁。是声在于政也。吾安知谁之所为乎。余曰。若尝观乎风乎。夫风塕然起于土囊之口。仿佯乎太虚。草木遇之而披拂。江海遇之而荡潏。金触之而铮铮然。玉触之而锵锵然。吹一耳声者万也。各以其形鸣焉。由是观之。谓之出于鼓可也。鼓者笑曰。是亦有鸣之者也。虽然。春之风和。夏之风燠。秋之风瑟如。冬之风觱如。风亦不能自为也。孰知其所以然。孰知夫声之所自。且击且歌。去而不顾。诗解
人心之灵。发而为声。声藏于肉。机触而生。神与机合。应律成章。天假之风人。其鸣铿锵。譬如雷奋于夏。虫吟于秋。若或命之。不可得而休焉。故诗之为言。以时而名。人之为诗。与天偕行。不可有意。则离于真。不可无意。恐丧其神。若有若无。妙在其间。玄乎微哉。言不能传。旨在辞表。象寓境先。如伏卵鸡。如蜕壳蝉。释智忘形。乃邻自然。情与物胶。人也非天。虚中之籁。月中之光。良玉有辉。名花生香。孰知其自。孰宰其功。为我问之无倪之翁。
格物解
格之为文。两木相薄之谓。周语曰。谷洛斗。韦昭解云
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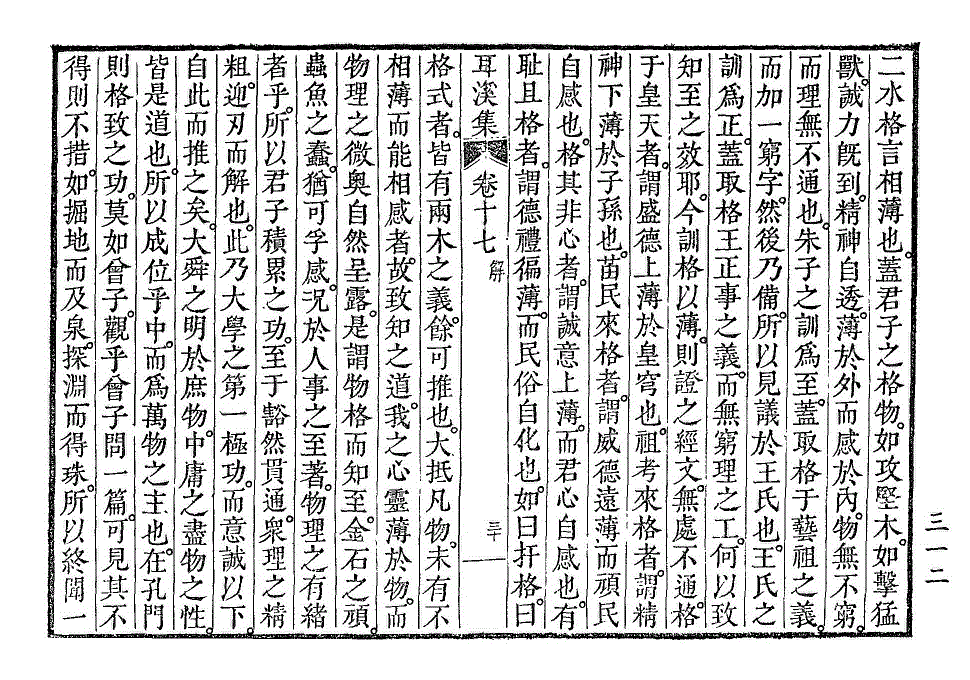 二水格言相薄也。盖君子之格物。如攻坚木。如击猛兽。诚力既到。精神自透。薄于外而感于内。物无不穷。而理无不通也。朱子之训为至。盖取格于艺祖之义。而加一穷字。然后乃备。所以见议于王氏也。王氏之训为正。盖取格王正事之义。而无穷理之工。何以致知至之效耶。今训格以薄。则證之经文。无处不通。格于皇天者。谓盛德上薄于皇穹也。祖考来格者。谓精神下薄于子孙也。苗民来格者。谓威德远薄而顽民自感也。格其非心者。谓诚意上薄。而君心自感也。有耻且格者。谓德礼遍薄。而民俗自化也。如曰捍格。曰格式者。皆有两木之义。馀可推也。大抵凡物。未有不相薄而能相感者。故致知之道。我之心灵薄于物。而物理之微奥自然呈露。是谓物格而知至。金石之顽。虫鱼之蠢。犹可孚感。况于人事之至著。物理之有绪者乎。所以君子积累之功。至于豁然贯通。众理之精粗。迎刃而解也。此乃大学之第一极功。而意诚以下。自此而推之矣。大舜之明于庶物。中庸之尽物之性。皆是道也。所以成位乎中。而为万物之主也。在孔门则格致之功。莫如曾子。观乎曾子问一篇。可见其不得则不措。如掘地而及泉。探渊而得珠。所以终闻一
二水格言相薄也。盖君子之格物。如攻坚木。如击猛兽。诚力既到。精神自透。薄于外而感于内。物无不穷。而理无不通也。朱子之训为至。盖取格于艺祖之义。而加一穷字。然后乃备。所以见议于王氏也。王氏之训为正。盖取格王正事之义。而无穷理之工。何以致知至之效耶。今训格以薄。则證之经文。无处不通。格于皇天者。谓盛德上薄于皇穹也。祖考来格者。谓精神下薄于子孙也。苗民来格者。谓威德远薄而顽民自感也。格其非心者。谓诚意上薄。而君心自感也。有耻且格者。谓德礼遍薄。而民俗自化也。如曰捍格。曰格式者。皆有两木之义。馀可推也。大抵凡物。未有不相薄而能相感者。故致知之道。我之心灵薄于物。而物理之微奥自然呈露。是谓物格而知至。金石之顽。虫鱼之蠢。犹可孚感。况于人事之至著。物理之有绪者乎。所以君子积累之功。至于豁然贯通。众理之精粗。迎刃而解也。此乃大学之第一极功。而意诚以下。自此而推之矣。大舜之明于庶物。中庸之尽物之性。皆是道也。所以成位乎中。而为万物之主也。在孔门则格致之功。莫如曾子。观乎曾子问一篇。可见其不得则不措。如掘地而及泉。探渊而得珠。所以终闻一耳溪集卷十七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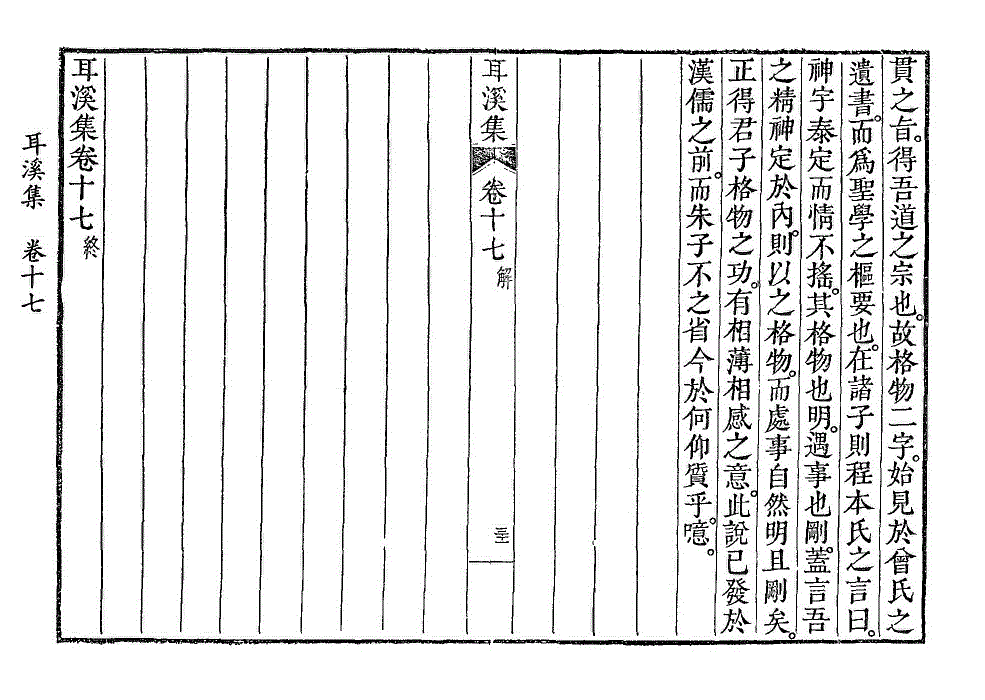 贯之旨。得吾道之宗也。故格物二字。始见于曾氏之遗书。而为圣学之枢要也。在诸子则程本氏之言曰。神宇泰定而情不摇。其格物也明。遇事也刚。盖言吾之精神定于内。则以之格物。而处事自然明且刚矣。正得君子格物之功。有相薄相感之意。此说已发于汉儒之前。而朱子不之省今于何仰质乎。噫。
贯之旨。得吾道之宗也。故格物二字。始见于曾氏之遗书。而为圣学之枢要也。在诸子则程本氏之言曰。神宇泰定而情不摇。其格物也明。遇事也刚。盖言吾之精神定于内。则以之格物。而处事自然明且刚矣。正得君子格物之功。有相薄相感之意。此说已发于汉儒之前。而朱子不之省今于何仰质乎。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