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耳溪集卷十三 第 x 页
耳溪集卷十三
记
记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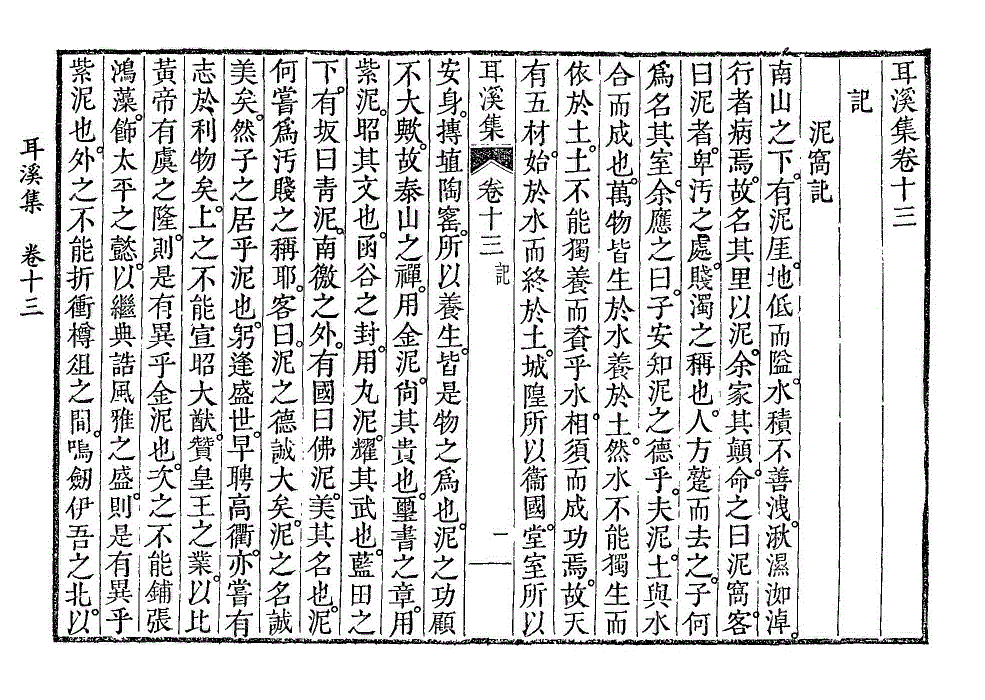 泥窝记
泥窝记南山之下。有泥厓。地低而隘。水积不善泄。湫湿洳淖。行者病焉。故名其里以泥。余家其颠。命之曰泥窝。客曰泥者。卑污之处。贱浊之称也。人方蹴而去之。子何为名其室。余应之曰。子安知泥之德乎。夫泥。土与水合而成也。万物皆生于水养于土。然水不能独生而依于土。土不能独养而资乎水。相须而成功焉。故天有五材。始于水而终于土。城隍所以卫国。堂室所以安身。抟埴陶窑。所以养生。皆是物之为也。泥之功顾不大欤。故泰山之禅。用金泥。尚其贵也。玺书之章。用紫泥。昭其文也。函谷之封。用丸泥。耀其武也。蓝田之下。有坂曰青泥。南徼之外。有国曰佛泥。美其名也。泥何尝为污贱之称耶。客曰。泥之德诚大矣。泥之名诚美矣。然子之居乎泥也。躬逢盛世。早聘高衢。亦尝有志于利物矣。上之不能宣昭大猷。赞皇王之业。以比黄帝有虞之隆。则是有异乎金泥也。次之不能铺张鸿藻。饰太平之懿。以继典诰风雅之盛。则是有异乎紫泥也。外之不能折冲樽俎之间。鸣剑伊吾之北。以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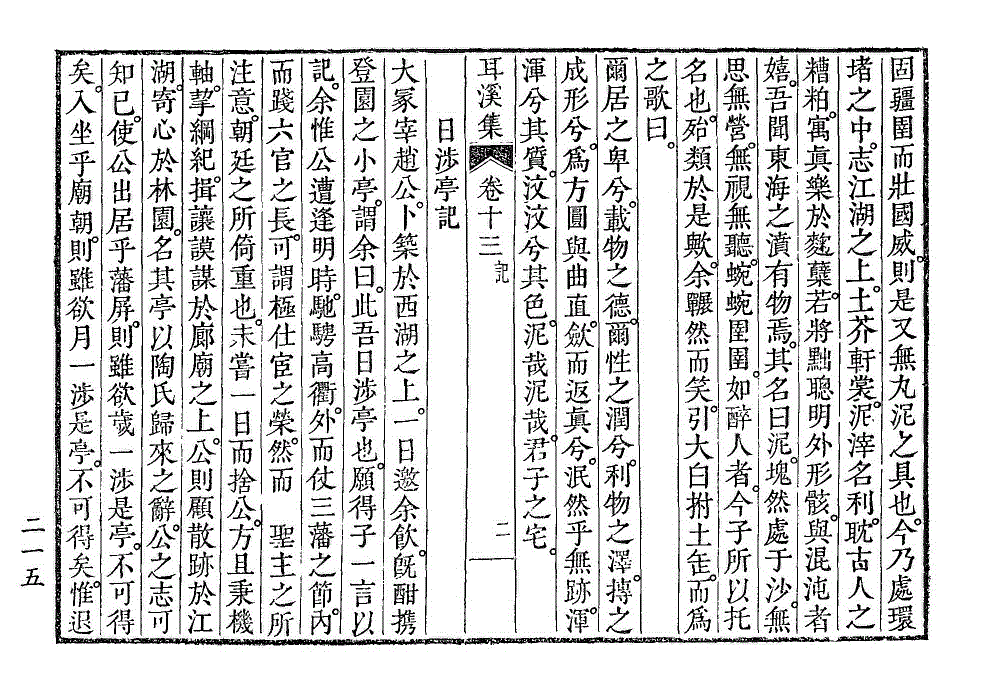 固疆圉而壮国威。则是又无丸泥之具也。今乃处环堵之中。志江湖之上。土芥轩裳。泥滓名利。耽古人之糟粕。寓真乐于曲糵。若将黜聪明外形骸。与混沌者嬉。吾闻东海之濆有物焉。其名曰泥。块然处于沙。无思无营。无视无听。蜿蜿圉圉。如醉人者。今子所以托名也。殆类于是欤。余冁然而笑。引大白拊土缶。而为之歌曰。
固疆圉而壮国威。则是又无丸泥之具也。今乃处环堵之中。志江湖之上。土芥轩裳。泥滓名利。耽古人之糟粕。寓真乐于曲糵。若将黜聪明外形骸。与混沌者嬉。吾闻东海之濆有物焉。其名曰泥。块然处于沙。无思无营。无视无听。蜿蜿圉圉。如醉人者。今子所以托名也。殆类于是欤。余冁然而笑。引大白拊土缶。而为之歌曰。尔居之卑兮。载物之德。尔性之润兮。利物之泽。抟之成形兮。为方圆与曲直。敛而返真兮。泯然乎无迹。浑浑兮其质。汶汶兮其色。泥哉泥哉。君子之宅。
日涉亭记
大冢宰赵公。卜筑于西湖之上。一日邀余饮。既酣携登园之小亭。谓余曰。此吾日涉亭也。愿得子一言以记。余惟公遭逢明时。驰骋高衢。外而仗三藩之节。内而践六官之长。可谓极仕宦之荣。然而 圣主之所注意。朝廷之所倚重也。未尝一日而舍公。方且秉机轴。挈纲纪。揖让谟谋于廊庙之上。公则顾散迹于江湖。寄心于林园。名其亭以陶氏归来之辞。公之志可知已。使公出居乎藩屏。则虽欲岁一涉是亭。不可得矣。入坐乎庙朝。则虽欲月一涉是亭。不可得矣。惟退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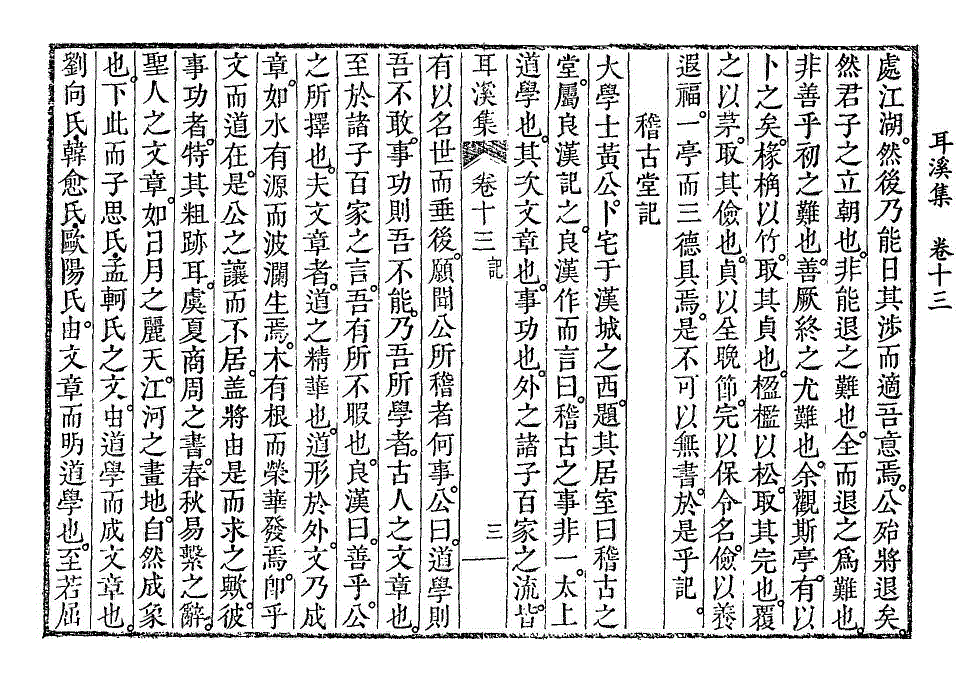 处江湖。然后乃能日其涉而适吾意焉。公殆将退矣。然君子之立朝也。非能退之难也。全而退之为难也。非善乎初之难也。善厥终之尤难也。余观斯亭。有以卜之矣。椽桷以竹。取其贞也。楹槛以松。取其完也。覆之以茅。取其俭也。贞以全晚节。完以保令名。俭以养遐福。一亭而三德具焉。是不可以无书。于是乎记。
处江湖。然后乃能日其涉而适吾意焉。公殆将退矣。然君子之立朝也。非能退之难也。全而退之为难也。非善乎初之难也。善厥终之尤难也。余观斯亭。有以卜之矣。椽桷以竹。取其贞也。楹槛以松。取其完也。覆之以茅。取其俭也。贞以全晚节。完以保令名。俭以养遐福。一亭而三德具焉。是不可以无书。于是乎记。稽古堂记
大学士黄公。卜宅于汉城之西。题其居室曰稽古之堂。属良汉记之。良汉作而言曰。稽古之事非一。太上道学也。其次文章也。事功也。外之诸子百家之流。皆有以名世而垂后。愿闻公所稽者何事。公曰。道学则吾不敢。事功则吾不能。乃吾所学者。古人之文章也。至于诸子百家之言。吾有所不暇也。良汉曰。善乎。公之所择也。夫文章者。道之精华也。道形于外。文乃成章。如水有源而波澜生焉。木有根而荣华发焉。即乎文而道在。是公之让而不居。盖将由是而求之欤。彼事功者。特其粗迹耳。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易系之辞。圣人之文章。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画地。自然成象也。下此而子思氏,孟轲氏之文。由道学而成文章也。刘向氏,韩愈氏,欧阳氏。由文章而明道学也。至若屈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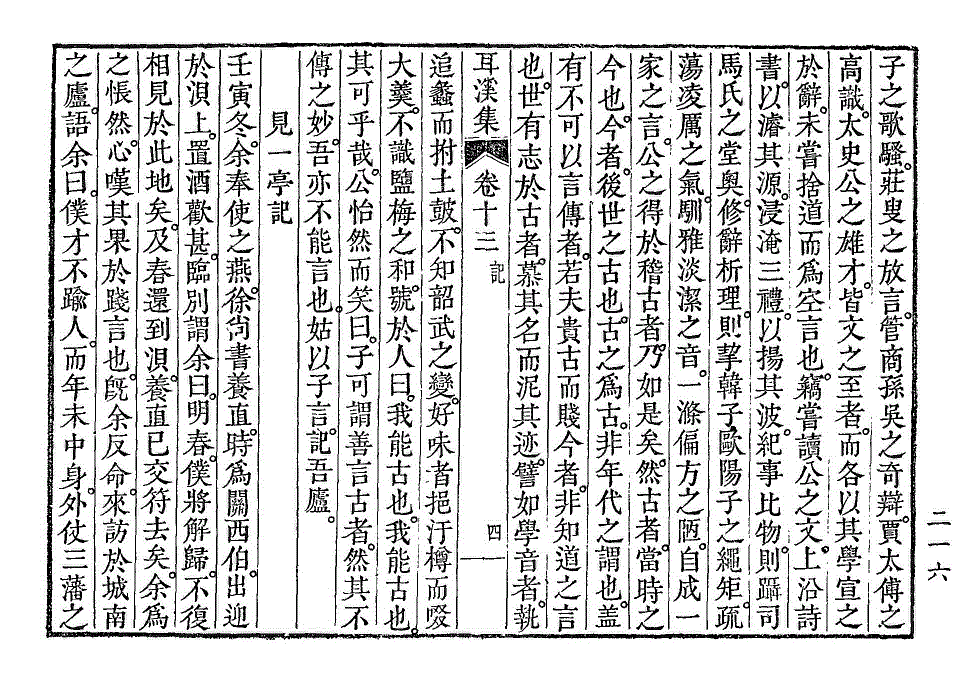 子之歌骚。庄叟之放言。管商孙吴之奇辩。贾太傅之高识。太史公之雄才。皆文之至者。而各以其学宣之于辞。未尝舍道而为空言也。窃尝读公之文。上沿诗书。以浚其源。浸淹三礼。以扬其波。纪事比物。则蹑司马氏之堂奥。修辞析理。则挈韩子,欧阳子之绳矩。疏荡凌厉之气。驯雅淡洁之音。一涤偏方之陋。自成一家之言。公之得于稽古者。乃如是矣。然古者。当时之今也。今者。后世之古也。古之为古。非年代之谓也。盖有不可以言传者。若夫贵古而贱今者。非知道之言也。世有志于古者。慕其名而泥其迹。譬如学音者。执追蠡而拊土鼓。不知韶武之变。好味者挹污樽而啜大羹。不识盐梅之和。号于人曰。我能古也。我能古也。其可乎哉。公怡然而笑曰。子可谓善言古者。然其不传之妙。吾亦不能言也。姑以子言。记吾庐。
子之歌骚。庄叟之放言。管商孙吴之奇辩。贾太傅之高识。太史公之雄才。皆文之至者。而各以其学宣之于辞。未尝舍道而为空言也。窃尝读公之文。上沿诗书。以浚其源。浸淹三礼。以扬其波。纪事比物。则蹑司马氏之堂奥。修辞析理。则挈韩子,欧阳子之绳矩。疏荡凌厉之气。驯雅淡洁之音。一涤偏方之陋。自成一家之言。公之得于稽古者。乃如是矣。然古者。当时之今也。今者。后世之古也。古之为古。非年代之谓也。盖有不可以言传者。若夫贵古而贱今者。非知道之言也。世有志于古者。慕其名而泥其迹。譬如学音者。执追蠡而拊土鼓。不知韶武之变。好味者挹污樽而啜大羹。不识盐梅之和。号于人曰。我能古也。我能古也。其可乎哉。公怡然而笑曰。子可谓善言古者。然其不传之妙。吾亦不能言也。姑以子言。记吾庐。见一亭记
壬寅冬。余奉使之燕。徐尚书养直。时为关西伯。出迎于浿上。置酒欢甚。临别谓余曰。明春。仆将解归。不复相见于此地矣。及春还到浿。养直已交符去矣。余为之怅然。心叹其果于践言也。既余反命。来访于城南之庐。语余曰。仆才不踰人。而年未中身。外仗三藩之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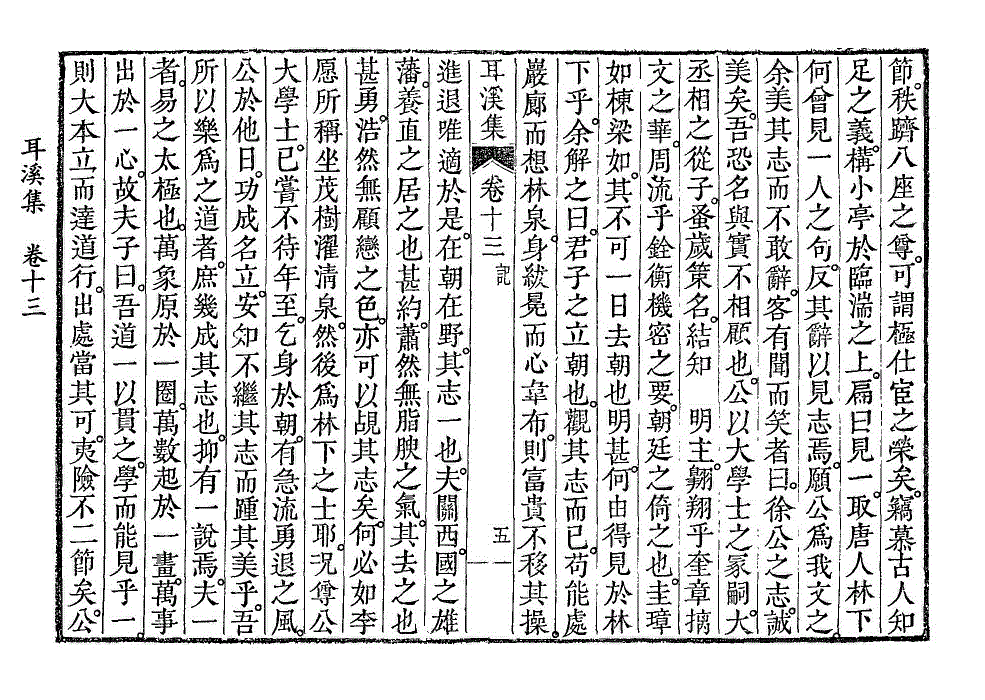 节。秩跻八座之尊。可谓极仕宦之荣矣。窃慕古人知足之义。构小亭于临湍之上。扁曰见一。取唐人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反其辞以见志焉。愿公为我文之。余美其志而不敢辞。客有闻而笑者曰。徐公之志。诚美矣。吾恐名与实不相顾也。公以大学士之冢嗣。大丞相之从子。蚤岁策名。结知 明主。翱翔乎奎章摛文之华。周流乎铨衡机密之要。朝廷之倚之也。圭璋如栋梁如。其不可一日去朝也明甚。何由得见于林下乎。余解之曰。君子之立朝也。观其志而已。苟能处岩廊而想林泉。身绂冕而心韦布。则富贵不移其操。进退唯适于是。在朝在野。其志一也。夫关西。国之雄藩。养直之居之也甚约。萧然无脂腴之气。其去之也甚勇。浩然无顾恋之色。亦可以觇其志矣。何必如李愿所称坐茂树濯清泉。然后为林下之士耶。况尊公大学士。已尝不待年至。乞身于朝。有急流勇退之风。公于他日。功成名立。安知不继其志而踵其美乎。吾所以乐为之道者。庶几成其志也。抑有一说焉。夫一者。易之太极也。万象原于一圈。万数起于一画。万事出于一心。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学而能见乎一。则大本立而达道行。出处当其可。夷险不二节矣。公
节。秩跻八座之尊。可谓极仕宦之荣矣。窃慕古人知足之义。构小亭于临湍之上。扁曰见一。取唐人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反其辞以见志焉。愿公为我文之。余美其志而不敢辞。客有闻而笑者曰。徐公之志。诚美矣。吾恐名与实不相顾也。公以大学士之冢嗣。大丞相之从子。蚤岁策名。结知 明主。翱翔乎奎章摛文之华。周流乎铨衡机密之要。朝廷之倚之也。圭璋如栋梁如。其不可一日去朝也明甚。何由得见于林下乎。余解之曰。君子之立朝也。观其志而已。苟能处岩廊而想林泉。身绂冕而心韦布。则富贵不移其操。进退唯适于是。在朝在野。其志一也。夫关西。国之雄藩。养直之居之也甚约。萧然无脂腴之气。其去之也甚勇。浩然无顾恋之色。亦可以觇其志矣。何必如李愿所称坐茂树濯清泉。然后为林下之士耶。况尊公大学士。已尝不待年至。乞身于朝。有急流勇退之风。公于他日。功成名立。安知不继其志而踵其美乎。吾所以乐为之道者。庶几成其志也。抑有一说焉。夫一者。易之太极也。万象原于一圈。万数起于一画。万事出于一心。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学而能见乎一。则大本立而达道行。出处当其可。夷险不二节矣。公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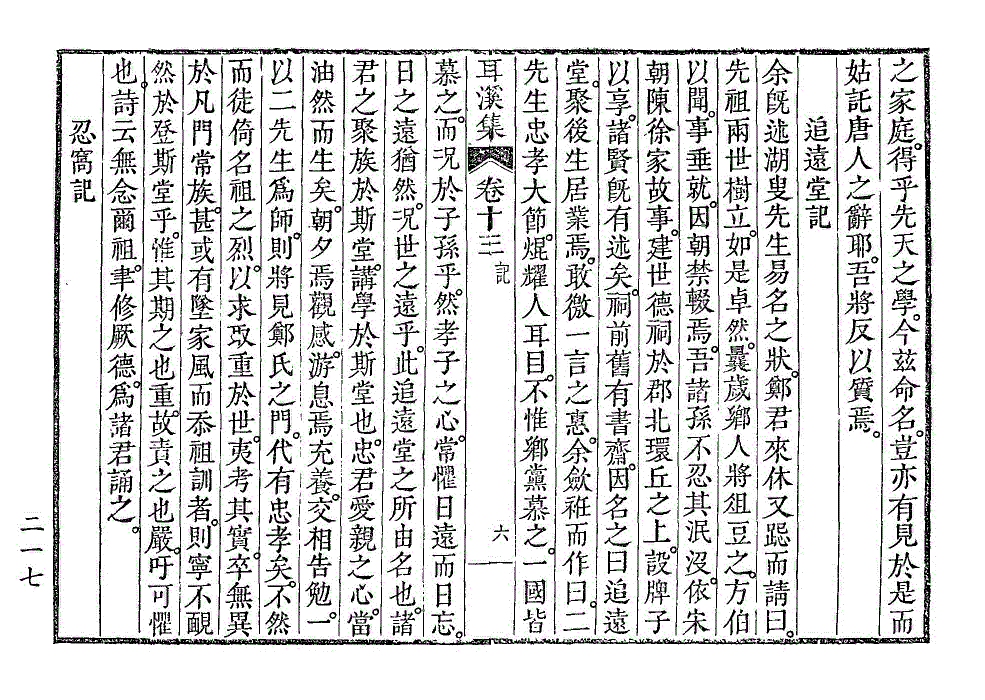 之家庭。得乎先天之学。今玆命名。岂亦有见于是而姑托唐人之辞耶。吾将反以质焉。
之家庭。得乎先天之学。今玆命名。岂亦有见于是而姑托唐人之辞耶。吾将反以质焉。追远堂记
余既述湖叟先生易名之状。郑君来休又跽而请曰。先祖两世树立。如是卓然。曩岁乡人将俎豆之。方伯以闻。事垂就。因朝禁辍焉。吾诸孙不忍其泯没。依宋朝陈徐家故事。建世德祠于郡北环丘之上。设牌子以享。诸贤既有述矣。祠前旧有书斋。因名之曰追远堂。聚后生居业焉。敢徼一言之惠。余敛衽而作曰。二先生忠孝大节。焜耀人耳目。不惟乡党慕之。一国皆慕之。而况于子孙乎。然孝子之心。常惧日远而日忘。日之远犹然。况世之远乎。此追远堂之所由名也。诸君之聚族于斯堂。讲学于斯堂也。忠君爱亲之心。当油然而生矣。朝夕焉观感。游息焉充养。交相告勉。一以二先生为师。则将见郑氏之门。代有忠孝矣。不然而徒倚名祖之烈。以求取重于世。夷考其实。卒无异于凡门常族。甚或有坠家风而忝祖训者。则宁不腼然于登斯堂乎。惟其期之也重。故责之也严。吁可惧也。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为诸君诵之。
忍窝记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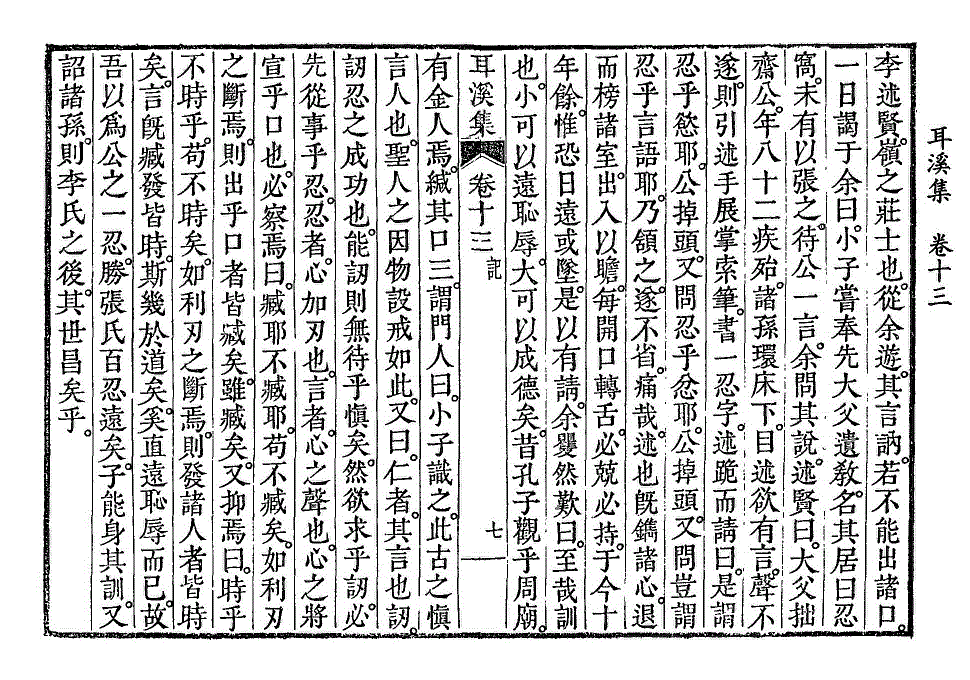 李述贤。岭之庄士也。从余游。其言讷。若不能出诸口。一日谒于余曰。小子尝奉先大父遗教。名其居曰忍窝。未有以张之。待公一言。余问其说。述贤曰。大父拙斋公。年八十二疾殆。诸孙环床下。目述欲有言。声不遂。则引述手展掌索笔。书一忍字。述跪而请曰。是谓忍乎欲耶。公掉头。又问忍乎忿耶。公掉头。又问岂谓忍乎言语耶。乃颔之。遂不省。痛哉。述也既镌诸心。退而榜诸室。出入以瞻。每开口转舌。必兢必持。于今十年馀。惟恐日远或坠。是以有请。余矍然叹曰。至哉训也。小可以远耻辱。大可以成德矣。昔孔子观乎周庙。有金人焉。缄其口三。谓门人曰。小子识之。此古之慎言人也。圣人之因物设戒如此。又曰。仁者。其言也讱。讱忍之成功也。能讱则无待乎慎矣。然欲求乎讱。必先从事乎忍。忍者。心加刃也。言者。心之声也。心之将宣乎口也。必察焉曰。臧耶不臧耶。苟不臧矣。如利刃之断焉。则出乎口者皆臧矣。虽臧矣。又抑焉曰。时乎不时乎。苟不时矣。如利刃之断焉。则发诸人者皆时矣。言既臧发皆时。斯几于道矣。奚直远耻辱而已。故吾以为公之一忍。胜张氏百忍远矣。子能身其训。又诏诸孙。则李氏之后。其世昌矣乎。
李述贤。岭之庄士也。从余游。其言讷。若不能出诸口。一日谒于余曰。小子尝奉先大父遗教。名其居曰忍窝。未有以张之。待公一言。余问其说。述贤曰。大父拙斋公。年八十二疾殆。诸孙环床下。目述欲有言。声不遂。则引述手展掌索笔。书一忍字。述跪而请曰。是谓忍乎欲耶。公掉头。又问忍乎忿耶。公掉头。又问岂谓忍乎言语耶。乃颔之。遂不省。痛哉。述也既镌诸心。退而榜诸室。出入以瞻。每开口转舌。必兢必持。于今十年馀。惟恐日远或坠。是以有请。余矍然叹曰。至哉训也。小可以远耻辱。大可以成德矣。昔孔子观乎周庙。有金人焉。缄其口三。谓门人曰。小子识之。此古之慎言人也。圣人之因物设戒如此。又曰。仁者。其言也讱。讱忍之成功也。能讱则无待乎慎矣。然欲求乎讱。必先从事乎忍。忍者。心加刃也。言者。心之声也。心之将宣乎口也。必察焉曰。臧耶不臧耶。苟不臧矣。如利刃之断焉。则出乎口者皆臧矣。虽臧矣。又抑焉曰。时乎不时乎。苟不时矣。如利刃之断焉。则发诸人者皆时矣。言既臧发皆时。斯几于道矣。奚直远耻辱而已。故吾以为公之一忍。胜张氏百忍远矣。子能身其训。又诏诸孙。则李氏之后。其世昌矣乎。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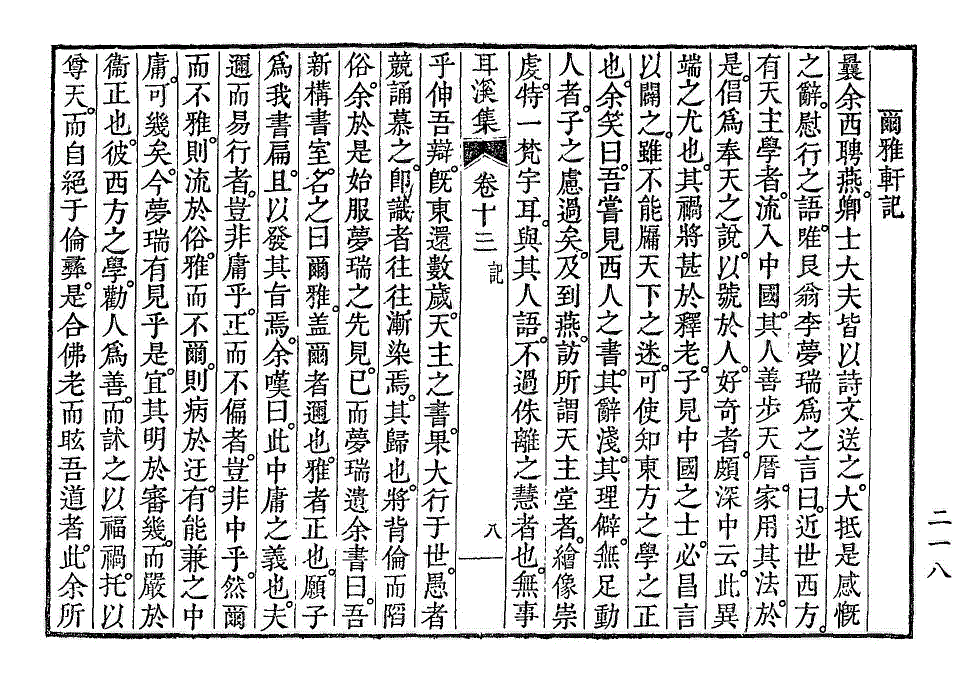 尔雅轩记
尔雅轩记曩余西聘燕。卿士大夫皆以诗文送之。大抵是感慨之辞。慰行之语。唯艮翁李梦瑞为之言曰。近世西方。有天主学者。流入中国。其人善步天历。家用其法。于是。倡为奉天之说。以号于人。好奇者。颇深中云。此异端之尤也。其祸将甚于释老。子见中国之士。必昌言以辟之。虽不能牖天下之迷。可使知东方之学之正也。余笑曰。吾尝见西人之书。其辞浅。其理僻。无足动人者。子之虑过矣。及到燕。访所谓天主堂者。绘像崇虔。特一梵宇耳。与其人语。不过侏离之慧者也。无事乎伸吾辩。既东还数岁。天主之书。果大行于世。愚者竞诵慕之。即识者往往渐染焉。其归也。将背伦而陷俗。余于是始服梦瑞之先见。已而梦瑞遗余书曰。吾新构书室。名之曰尔雅。盖尔者迩也。雅者正也。愿子为我书扁。且以发其旨焉。余叹曰。此中庸之义也。夫迩而易行者。岂非庸乎。正而不偏者。岂非中乎。然尔而不雅。则流于俗。雅而不尔。则病于迂。有能兼之中庸。可几矣。今梦瑞有见乎是。宜其明于审几。而严于卫正也。彼西方之学。劝人为善。而訹之以福祸。托以尊天。而自绝于伦彝。是合佛老而眩吾道者。此余所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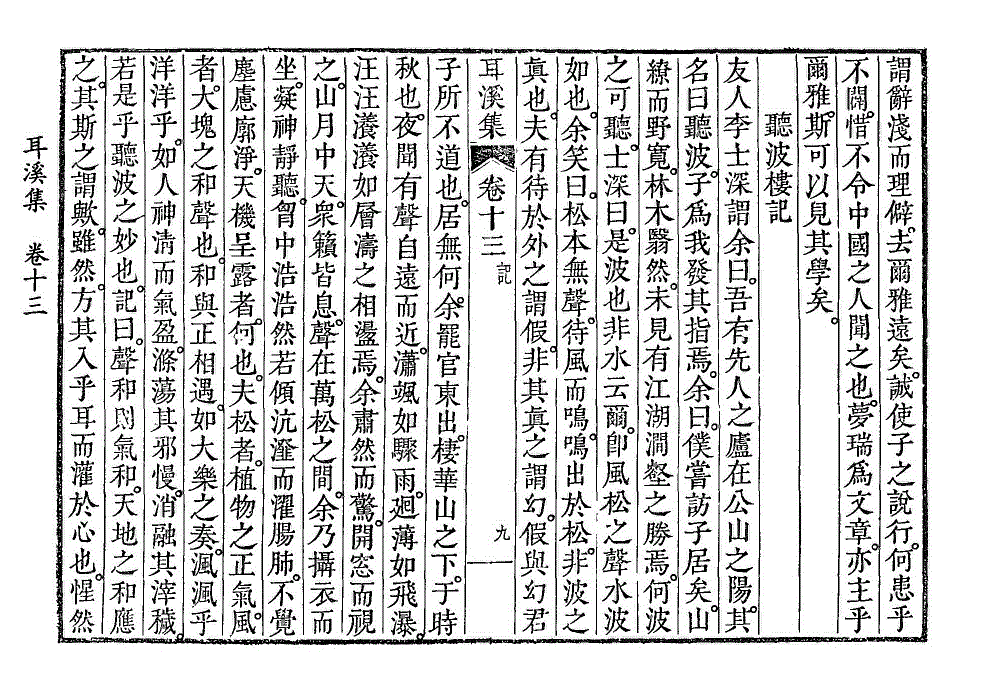 谓辞浅而理僻。去尔雅远矣。诚使子之说行。何患乎不辟。惜不令中国之人闻之也。梦瑞为文章。亦主乎尔雅。斯可以见其学矣。
谓辞浅而理僻。去尔雅远矣。诚使子之说行。何患乎不辟。惜不令中国之人闻之也。梦瑞为文章。亦主乎尔雅。斯可以见其学矣。听波楼记
友人李士深谓余曰。吾有先人之庐在公山之阳。其名曰听波。子为我发其指焉。余曰。仆尝访子居矣。山缭而野宽。林木翳然。未见有江湖涧壑之胜焉。何波之可听。士深曰。是波也非水云尔。即风松之声水波如也。余笑曰。松本无声。待风而鸣。鸣出于松。非波之真也。夫有待于外之谓假。非其真之谓幻。假与幻君子所不道也。居无何。余罢官东出。栖华山之下。于时秋也。夜闻有声自远而近。潇飒如骤雨。回薄如飞瀑。汪汪瀁瀁如层涛之相荡焉。余肃然而惊。开窗而视之。山月中天。众籁皆息。声在万松之间。余乃摄衣而坐。凝神静听。胸中浩浩然若倾沆瀣而濯肠肺。不觉尘虑廓净。天机呈露者。何也。夫松者。植物之正气。风者。大块之和声也。和与正相遇。如大乐之奏。沨沨乎洋洋乎。如人神清而气盈。涤荡其邪慢。消融其滓秽。若是乎听波之妙也。记曰。声和则气和。天地之和应之。其斯之谓欤。虽然。方其入乎耳而灌于心也。惺然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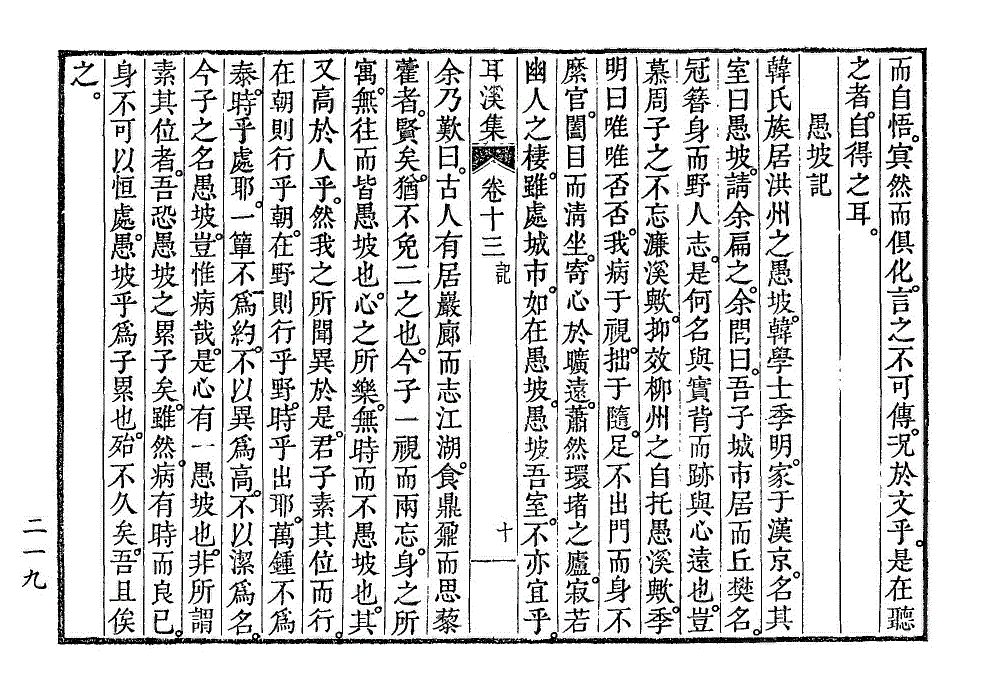 而自悟。冥然而俱化。言之不可传。况于文乎。是在听之者。自得之耳。
而自悟。冥然而俱化。言之不可传。况于文乎。是在听之者。自得之耳。愚坡记
韩氏族居洪州之愚坡。韩学士季明。家于汉京。名其室曰愚坡。请余扁之。余问曰。吾子城市居而丘樊名。冠簪身而野人志。是何名与实背而迹与心远也。岂慕周子之不忘濂溪欤。抑效柳州之自托愚溪欤。季明曰唯唯否否。我病于视。拙于随。足不出门而身不縻官。阖目而清坐。寄心于旷远。萧然环堵之庐。寂若幽人之栖。虽处城市。如在愚坡。愚坡吾室。不亦宜乎。余乃叹曰。古人有居岩廊而志江湖。食鼎鼐而思藜藿者。贤矣。犹不免二之也。今子一视而两忘。身之所寓。无往而皆愚坡也。心之所乐。无时而不愚坡也。其又高于人乎。然我之所闻异于是。君子素其位而行。在朝则行乎朝。在野则行乎野。时乎出耶。万钟不为泰。时乎处耶。一箪不为约。不以异为高。不以洁为名。今子之名愚坡。岂惟病哉。是心有一愚坡也。非所谓素其位者。吾恐愚坡之累子矣。虽然。病有时而良已。身不可以恒处。愚坡乎为子累也。殆不久矣。吾且俟之。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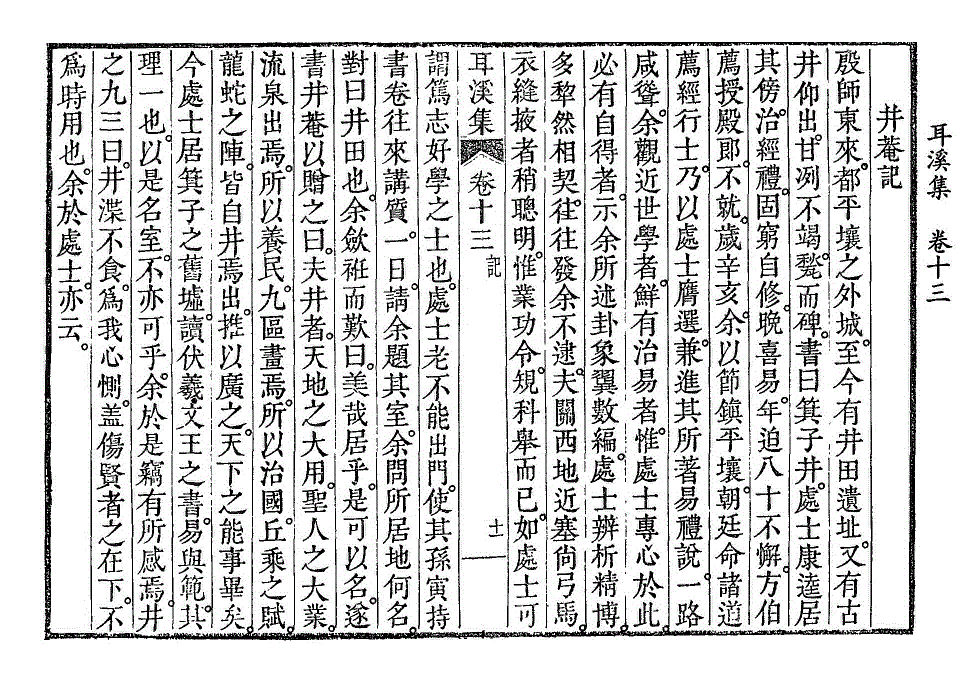 井庵记
井庵记殷师东来。都平壤之外城。至今有井田遗址。又有古井仰出。甘冽不竭。甃而碑。书曰箕子井。处士康逵居其傍。治经礼。固穷自修。晚喜易。年迫八十不懈。方伯荐授殿郎。不就。岁辛亥。余以节镇平壤。朝廷命诸道荐经行士。乃以处士膺选。兼进其所著易礼说。一路咸耸。余观近世学者。鲜有治易者。惟处士专心于此。必有自得者。示余所述卦象翼数编。处士辨析精博。多犁然相契。往往发余不逮。夫关西地近塞尚弓马。衣缝掖者稍聪明。惟业功令。规科举而已。如处士可谓笃志好学之士也。处士老不能出门。使其孙寅持书卷往来讲质。一日。请余题其室。余问所居地何名。对曰井田也。余敛衽而叹曰。美哉居乎。是可以名。遂书井庵以赠之曰。夫井者。天地之大用。圣人之大业。流泉出焉。所以养民。九区画焉。所以治国。丘乘之赋。龙蛇之阵。皆自井焉出。推以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今处士居箕子之旧墟。读伏羲,文王之书。易与范。其理一也。以是名室。不亦可乎。余于是窃有所感焉。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盖伤贤者之在下。不为时用也。余于处士。亦云。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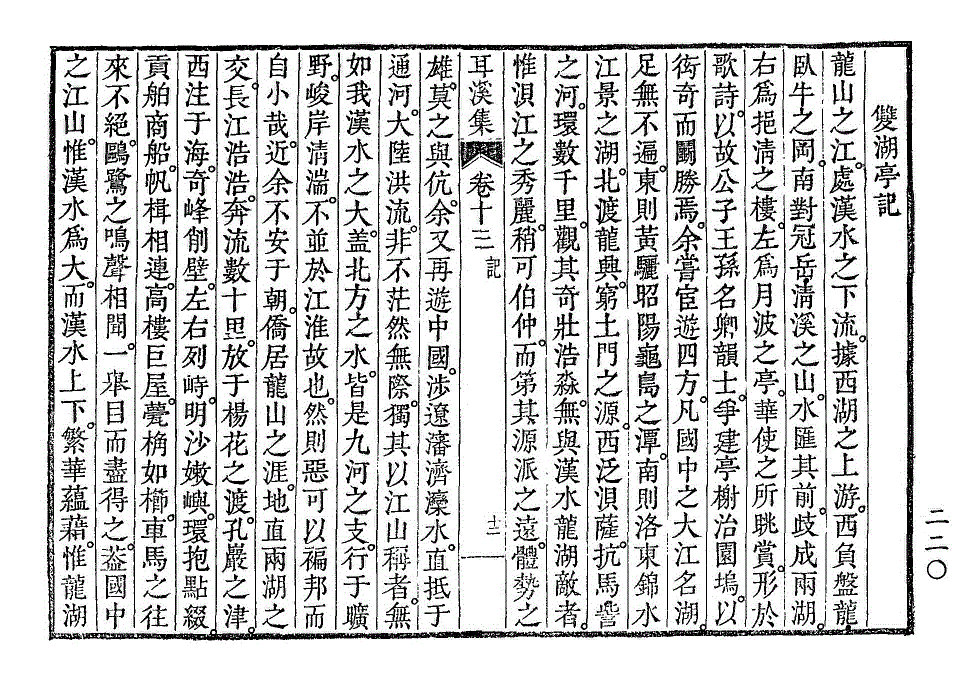 双湖亭记
双湖亭记龙山之江。处汉水之下流。据西湖之上游。西负盘龙,卧牛之冈。南对冠岳,清溪之山。水汇其前。歧成两湖。右为挹清之楼。左为月波之亭。华使之所眺赏。形于歌诗。以故公子王孙名卿韵士。争建亭榭治园坞。以衒奇而斗胜焉。余尝宦游四方。凡国中之大江名湖。足无不遍。东则黄骊昭阳龟岛之潭。南则洛东锦水江景之湖。北渡龙兴。穷土门之源。西泛浿萨。抗马訾之河。环数千里。观其奇壮浩淼。无与汉水龙湖敌者。惟浿江之秀丽。稍可伯仲。而第其源派之远。体势之雄。莫之与伉。余又再游中国。涉辽沈济滦水。直抵于通河。大陆洪流。非不茫然无际。独其以江山称者。无如我汉水之大。盖北方之水。皆是九河之支。行于旷野。峻岸清湍。不并于江淮故也。然则恶可以褊邦而自小哉。近余不安于朝。侨居龙山之涯。地直两湖之交。长江浩浩。奔流数十里。放于杨花之渡。孔岩之津。西注于海。奇峰削壁。左右列峙。明沙嫩屿。环抱点缀。贡舶商船。帆楫相连。高楼巨屋。甍桷如栉。车马之往来不绝。鸥鹭之鸣声相闻。一举目而尽得之。盖国中之江山。惟汉水为大。而汉水上下。繁华蕴藉。惟龙湖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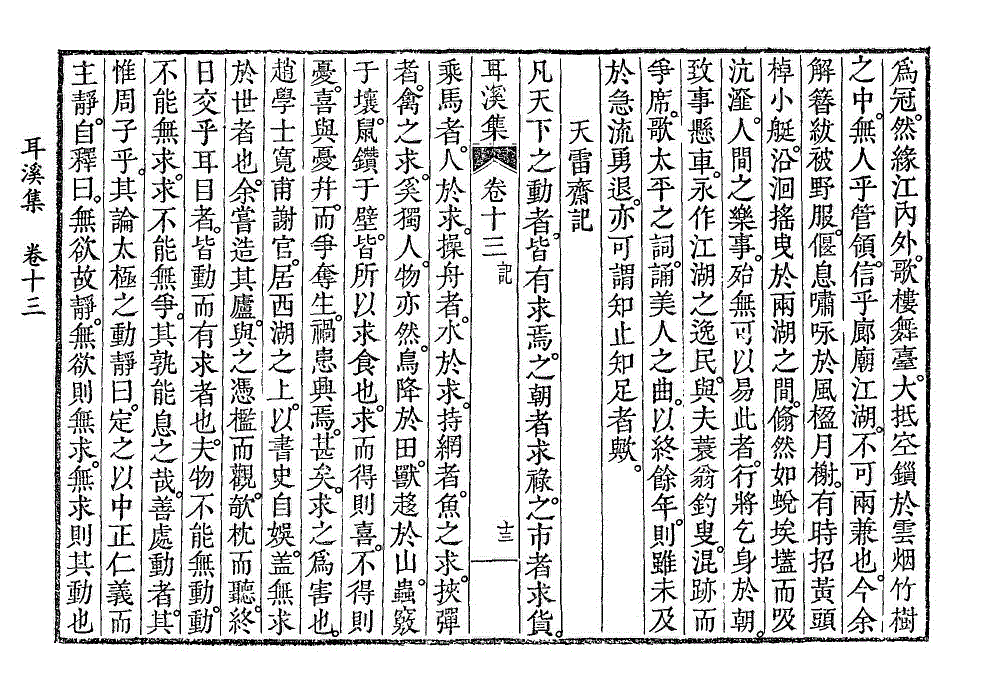 为冠。然缘江内外。歌楼舞台。大抵空锁于云烟竹树之中。无人乎管领。信乎廊庙江湖。不可两兼也。今余解簪绂被野服。偃息啸咏于风楹月榭。有时招黄头棹小艇。沿洄摇曳于两湖之间。翛然如蜕埃壒而吸沆瀣。人间之乐事。殆无可以易此者。行将乞身于朝。致事悬车。永作江湖之逸民。与夫蓑翁钓叟。混迹而争席。歌太平之词。诵美人之曲。以终馀年。则虽未及于急流勇退。亦可谓知止知足者欤。
为冠。然缘江内外。歌楼舞台。大抵空锁于云烟竹树之中。无人乎管领。信乎廊庙江湖。不可两兼也。今余解簪绂被野服。偃息啸咏于风楹月榭。有时招黄头棹小艇。沿洄摇曳于两湖之间。翛然如蜕埃壒而吸沆瀣。人间之乐事。殆无可以易此者。行将乞身于朝。致事悬车。永作江湖之逸民。与夫蓑翁钓叟。混迹而争席。歌太平之词。诵美人之曲。以终馀年。则虽未及于急流勇退。亦可谓知止知足者欤。天雷斋记
凡天下之动者。皆有求焉。之朝者求禄。之市者求货。乘马者。人于求。操舟者。水于求。持网者。鱼之求。挟弹者。禽之求。奚独人。物亦然。鸟降于田。兽趍于山。虫窍于壤。鼠钻于壁。皆所以求食也。求而得则喜。不得则忧。喜与忧并。而争夺生。祸患兴焉。甚矣。求之为害也。赵学士宽甫谢官。居西湖之上。以书史自娱。盖无求于世者也。余尝造其庐。与之凭槛而观。欹枕而听。终日交乎耳目者。皆动而有求者也。夫物不能无动。动不能无求。求不能无争。其孰能息之哉。善处动者。其惟周子乎。其论太极之动静曰。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释曰。无欲故静。无欲则无求。无求则其动也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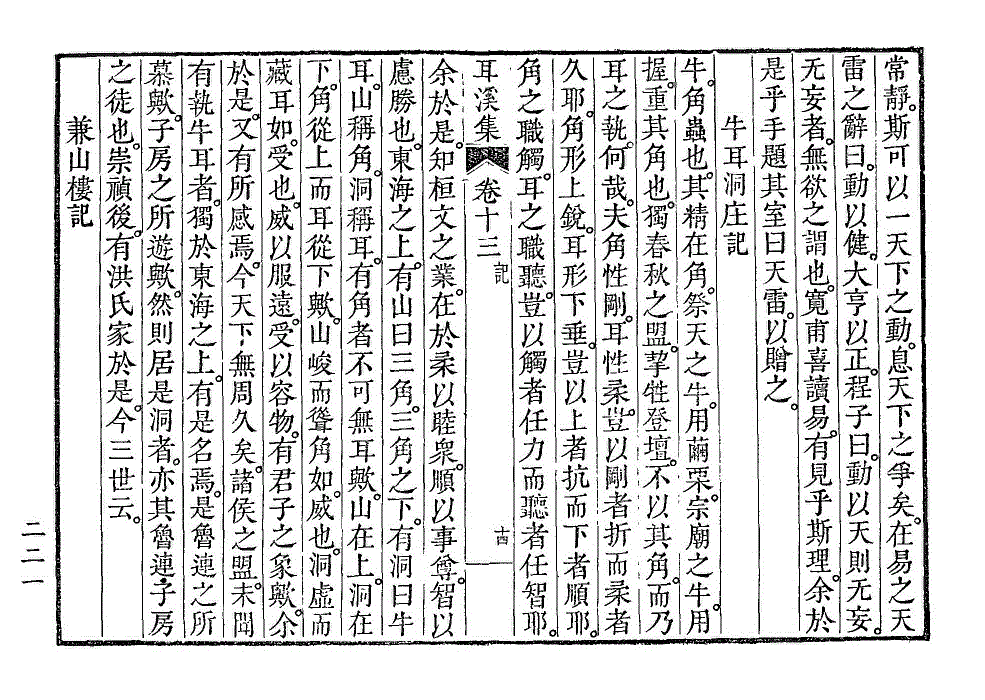 常静。斯可以一天下之动。息天下之争矣。在易之天雷之辞曰。动以健。大亨以正。程子曰。动以天则无妄。无妄者。无欲之谓也。宽甫喜读易。有见乎斯理。余于是乎手题其室曰天雷。以赠之。
常静。斯可以一天下之动。息天下之争矣。在易之天雷之辞曰。动以健。大亨以正。程子曰。动以天则无妄。无妄者。无欲之谓也。宽甫喜读易。有见乎斯理。余于是乎手题其室曰天雷。以赠之。牛耳洞庄记
牛。角虫也。其精在角。祭天之牛。用茧栗。宗庙之牛。用握。重其角也。独春秋之盟。挈牲登坛。不以其角。而乃耳之执。何哉。夫角性刚。耳性柔。岂以刚者折而柔者久耶。角形上锐。耳形下垂。岂以上者抗而下者顺耶。角之职触。耳之职听。岂以触者任力而听者任智耶。余于是。知桓文之业。在于柔以睦众。顺以事尊。智以虑胜也。东海之上。有山曰三角。三角之下。有洞曰牛耳。山称角。洞称耳。有角者不可无耳欤。山在上。洞在下。角从上而耳从下欤。山峻而耸角如。威也。洞虚而藏耳如。受也。威以服远。受以容物。有君子之象欤。余于是。又有所感焉。今天下无周久矣。诸侯之盟。未闻有执牛耳者。独于东海之上。有是名焉。是鲁连之所慕欤。子房之所游欤。然则居是洞者。亦其鲁连,子房之徒也。崇祯后。有洪氏家于是。今三世云。
兼山楼记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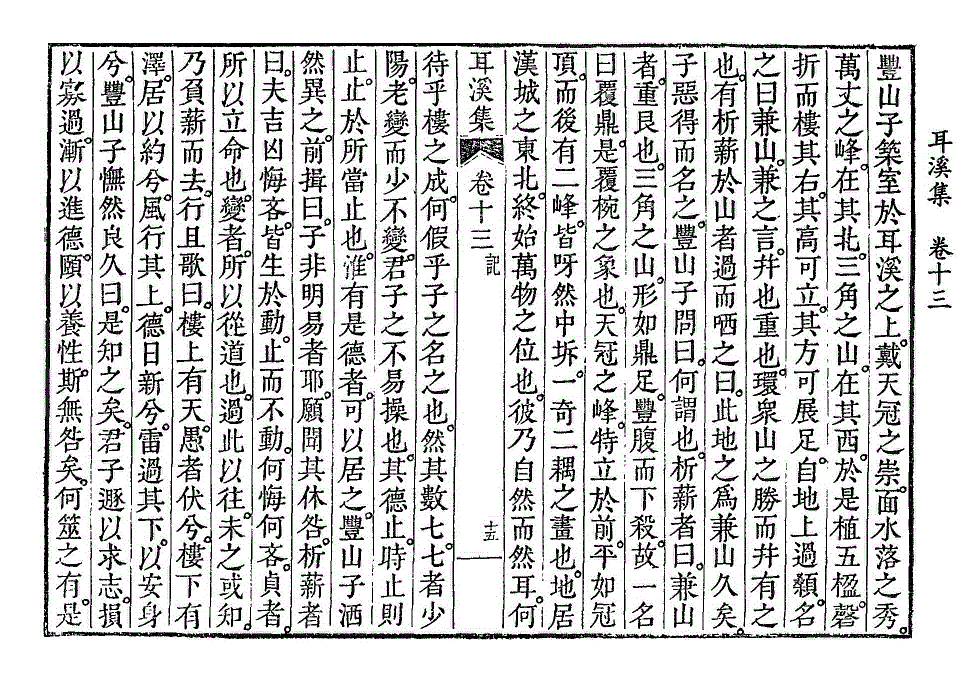 丰山子筑室于耳溪之上。戴天冠之崇。面水落之秀。万丈之峰。在其北。三角之山。在其西。于是植五楹。磬折而楼其右。其高可立。其方可展足。自地上过颡。名之曰兼山。兼之言。并也重也。环众山之胜而并有之也。有析薪于山者过而哂之曰。此地之为兼山久矣。子恶得而名之。丰山子问曰。何谓也。析薪者曰。兼山者。重艮也。三角之山。形如鼎足。丰腹而下杀。故一名曰覆鼎。是覆碗之象也。天冠之峰。特立于前。平如冠顶。而后有二峰。皆呀然中坼。一奇二耦之画也。地居汉城之东北。终始万物之位也。彼乃自然而然耳。何待乎楼之成。何假乎子之名之也。然其数七。七者少阳。老变而少不变。君子之不易操也。其德止。时止则止。止于所当止也。惟有是德者。可以居之。丰山子洒然异之。前揖曰。子非明易者耶。愿闻其休咎。析薪者曰。夫吉凶悔吝。皆生于动。止而不动。何悔何吝。贞者。所以立命也。变者。所以从道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乃负薪而去。行且歌曰。楼上有天。愚者伏兮。楼下有泽。居以约兮。风行其上。德日新兮。雷过其下。以安身兮。丰山子怃然良久曰。是知之矣。君子遁以求志。损以寡过。渐以进德。颐以养性。斯无咎矣。何筮之有。是
丰山子筑室于耳溪之上。戴天冠之崇。面水落之秀。万丈之峰。在其北。三角之山。在其西。于是植五楹。磬折而楼其右。其高可立。其方可展足。自地上过颡。名之曰兼山。兼之言。并也重也。环众山之胜而并有之也。有析薪于山者过而哂之曰。此地之为兼山久矣。子恶得而名之。丰山子问曰。何谓也。析薪者曰。兼山者。重艮也。三角之山。形如鼎足。丰腹而下杀。故一名曰覆鼎。是覆碗之象也。天冠之峰。特立于前。平如冠顶。而后有二峰。皆呀然中坼。一奇二耦之画也。地居汉城之东北。终始万物之位也。彼乃自然而然耳。何待乎楼之成。何假乎子之名之也。然其数七。七者少阳。老变而少不变。君子之不易操也。其德止。时止则止。止于所当止也。惟有是德者。可以居之。丰山子洒然异之。前揖曰。子非明易者耶。愿闻其休咎。析薪者曰。夫吉凶悔吝。皆生于动。止而不动。何悔何吝。贞者。所以立命也。变者。所以从道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乃负薪而去。行且歌曰。楼上有天。愚者伏兮。楼下有泽。居以约兮。风行其上。德日新兮。雷过其下。以安身兮。丰山子怃然良久曰。是知之矣。君子遁以求志。损以寡过。渐以进德。颐以养性。斯无咎矣。何筮之有。是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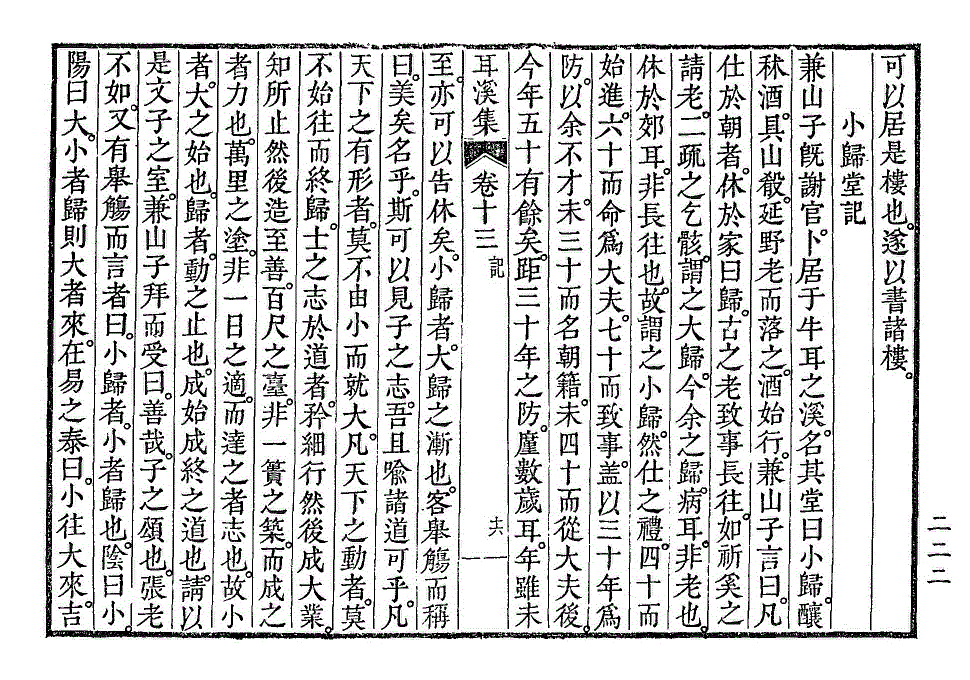 可以居是楼也。遂以书诸楼。
可以居是楼也。遂以书诸楼。小归堂记
兼山子既谢官。卜居于牛耳之溪。名其堂曰小归。酿秫酒。具山殽。延野老而落之。酒始行。兼山子言曰。凡仕于朝者。休于家曰归。古之老致事长往。如祈奚之请老。二疏之乞骸。谓之大归。今余之归。病耳。非老也。休于郊耳。非长往也。故谓之小归。然仕之礼。四十而始进。六十而命为大夫。七十而致事。盖以三十年为防。以余不才。未三十而名朝籍。未四十而从大夫后。今年五十有馀矣。距三十年之防。廑数岁耳。年虽未至。亦可以告休矣。小归者。大归之渐也。客举觞而称曰。美矣名乎。斯可以见子之志。吾且喻诸道可乎。凡天下之有形者。莫不由小而就大。凡天下之动者。莫不始往而终归。士之志于道者。矜细行然后成大业。知所止然后造至善。百尺之台。非一篑之筑。而成之者力也。万里之涂。非一日之适。而达之者志也。故小者。大之始也。归者。动之止也。成始成终之道也。请以是文子之室。兼山子拜而受曰。善哉。子之颂也。张老不如。又有举觞而言者曰。小归者。小者归也。阴曰小。阳曰大。小者归则大者来。在易之泰曰。小往大来。吉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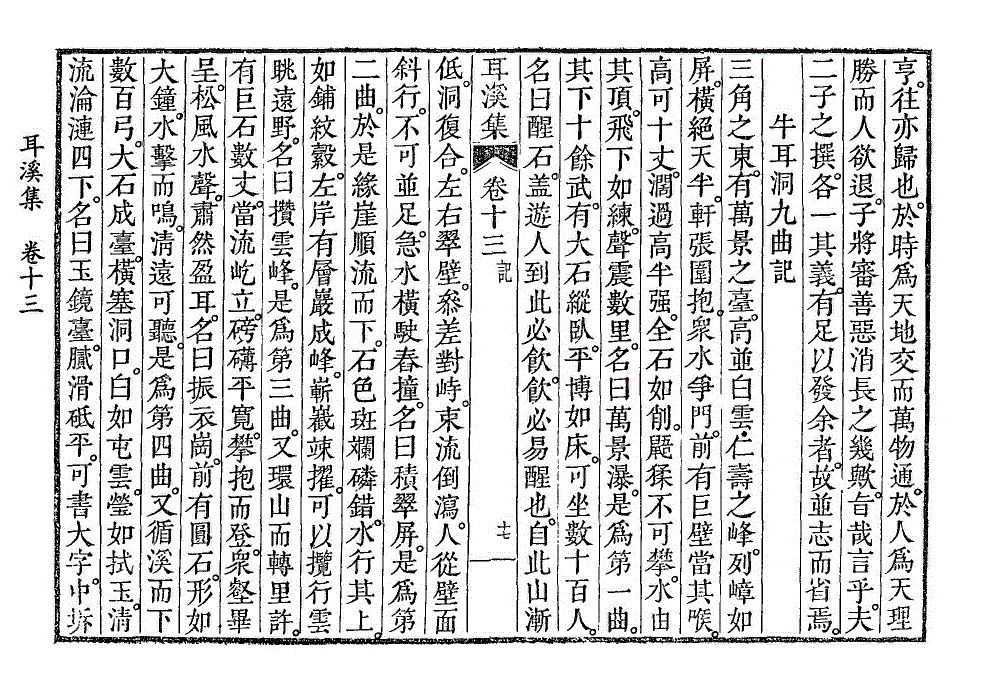 亨。往亦归也。于时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于人为天理胜而人欲退。子将审善恶消长之几欤。旨哉言乎。夫二子之撰。各一其义。有足以发余者。故并志而省焉。
亨。往亦归也。于时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于人为天理胜而人欲退。子将审善恶消长之几欤。旨哉言乎。夫二子之撰。各一其义。有足以发余者。故并志而省焉。牛耳洞九曲记
三角之东。有万景之台。高并白云,仁寿之峰。列嶂如屏。横绝天半。轩张围抱。众水争门。前有巨壁当其喉。高可十丈。阔过高半强。全石如削。鼯猱不可攀。水由其顶。飞下如练。声震数里。名曰万景瀑。是为第一曲。其下十馀武。有大石纵卧。平博如床。可坐数十百人。名曰醒石。盖游人到此必饮。饮必易醒也。自此山渐低。洞复合。左右翠壁。参差对峙。束流倒泻。人从壁面斜行。不可并足。急水横驶舂撞。名曰积翠屏。是为第二曲。于是缘崖顺流而下。石色斑斓磷错。水行其上。如铺纹縠。左岸有层岩成峰。崭巀竦擢。可以揽行云眺远野。名曰攒云峰。是为第三曲。又环山而转里许。有巨石数丈。当流屹立。磅礴平宽。攀抱而登。众壑毕呈。松风水声。肃然盈耳。名曰振衣岗。前有圆石。形如大钟。水击而鸣。清远可听。是为第四曲。又循溪而下数百弓。大石成台。横塞洞口。白如屯云。莹如拭玉。清流沦涟四下。名曰玉镜台。腻滑砥平。可书大字。中坼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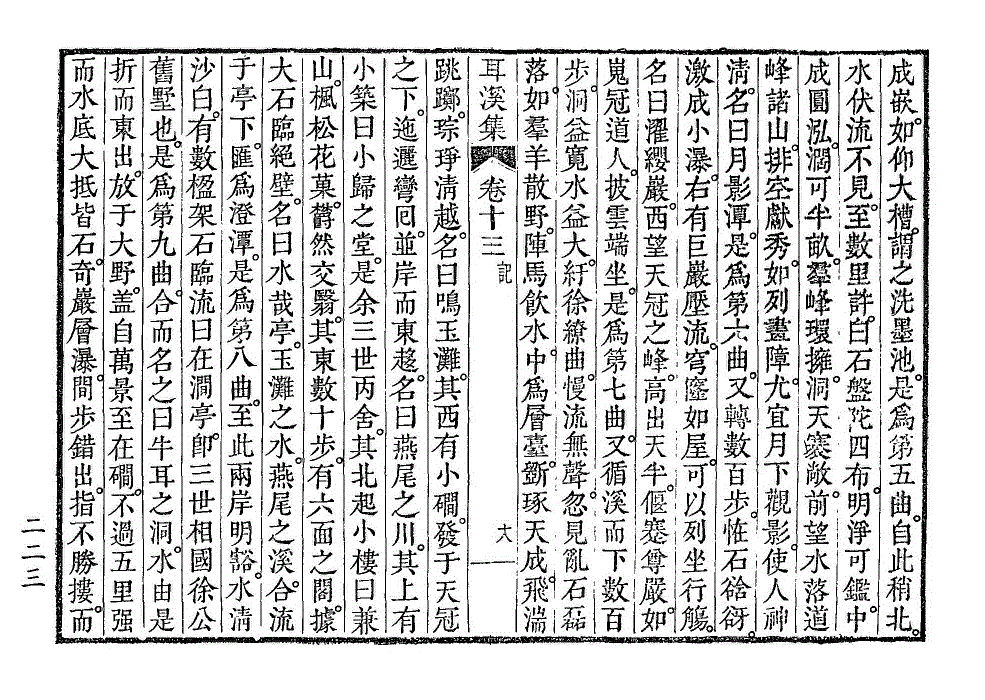 成嵌。如仰大槽。谓之洗墨池。是为第五曲。自此稍北。水伏流不见。至数里许。白石盘陀四布。明净可鉴。中成圆泓。阔可半亩。群峰环拥。洞天褰敞。前望水落,道峰诸山。排空献秀。如列画障。尤宜月下观影。使人神清。名曰月影潭。是为第六曲。又转数百步。怪石谽谺。激成小瀑。右有巨岩压流。穹窿如屋。可以列坐行觞。名曰濯缨岩。西望天冠之峰。高出天半。偃蹇尊严。如嵬冠道人。披云端坐。是为第七曲。又循溪而下数百步。洞益宽水益大。纡徐缭曲。慢流无声。忽见乱石磊落。如群羊散野。阵马饮水。中为层台。斲琢天成。飞湍跳踯。琮琤清越。名曰鸣玉滩。其西有小涧。发于天冠之下。迤逦弯回。并岸而东趍。名曰燕尾之川。其上有小筑曰小归之堂。是余三世丙舍。其北起小楼曰兼山。枫松花果。郁然交翳。其东数十步。有六面之阁。据大石临绝壁。名曰水哉亭。玉滩之水。燕尾之溪。合流于亭下。汇为澄潭。是为第八曲。至此两岸明豁。水清沙白。有数楹架石临流曰在涧亭。即三世相国徐公旧墅也。是为第九曲。合而名之曰牛耳之洞。水由是折而东出。放于大野。盖自万景至在涧。不过五里。强而水底大抵皆石。奇岩层瀑。间步错出。指不胜搂。而
成嵌。如仰大槽。谓之洗墨池。是为第五曲。自此稍北。水伏流不见。至数里许。白石盘陀四布。明净可鉴。中成圆泓。阔可半亩。群峰环拥。洞天褰敞。前望水落,道峰诸山。排空献秀。如列画障。尤宜月下观影。使人神清。名曰月影潭。是为第六曲。又转数百步。怪石谽谺。激成小瀑。右有巨岩压流。穹窿如屋。可以列坐行觞。名曰濯缨岩。西望天冠之峰。高出天半。偃蹇尊严。如嵬冠道人。披云端坐。是为第七曲。又循溪而下数百步。洞益宽水益大。纡徐缭曲。慢流无声。忽见乱石磊落。如群羊散野。阵马饮水。中为层台。斲琢天成。飞湍跳踯。琮琤清越。名曰鸣玉滩。其西有小涧。发于天冠之下。迤逦弯回。并岸而东趍。名曰燕尾之川。其上有小筑曰小归之堂。是余三世丙舍。其北起小楼曰兼山。枫松花果。郁然交翳。其东数十步。有六面之阁。据大石临绝壁。名曰水哉亭。玉滩之水。燕尾之溪。合流于亭下。汇为澄潭。是为第八曲。至此两岸明豁。水清沙白。有数楹架石临流曰在涧亭。即三世相国徐公旧墅也。是为第九曲。合而名之曰牛耳之洞。水由是折而东出。放于大野。盖自万景至在涧。不过五里。强而水底大抵皆石。奇岩层瀑。间步错出。指不胜搂。而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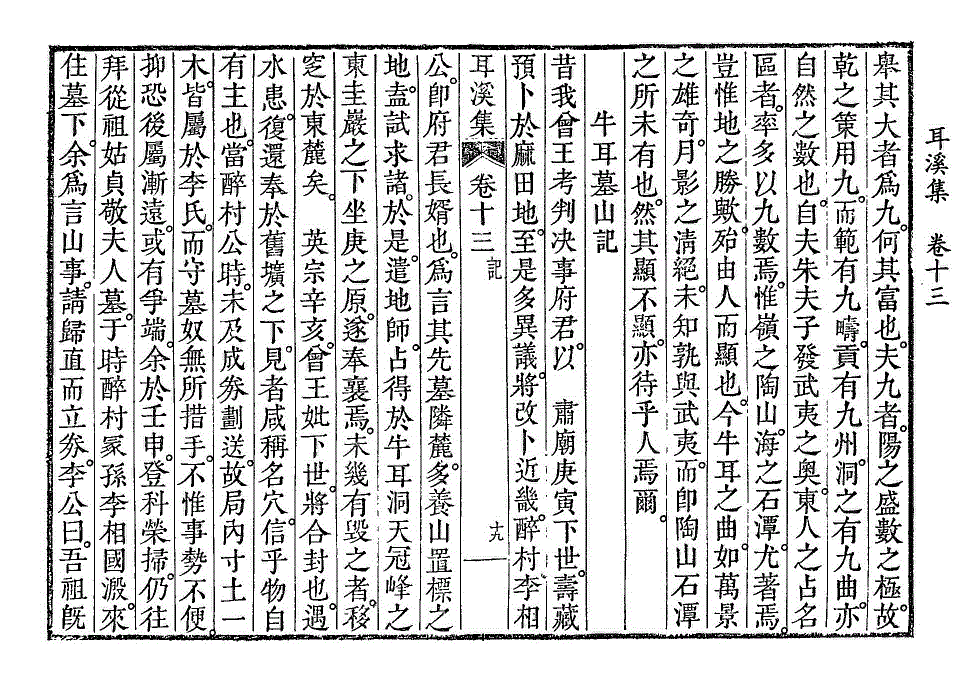 举其大者为九。何其富也。夫九者。阳之盛数之极。故乾之策用九。而范有九畴。贡有九州。洞之有九曲。亦自然之数也。自夫朱夫子发武夷之奥。东人之占名区者。率多以九数焉。惟岭之陶山。海之石潭。尤著焉。岂惟地之胜欤。殆由人而显也。今牛耳之曲。如万景之雄奇。月影之清绝。未知孰与武夷。而即陶山石潭之所未有也。然其显不显。亦待乎人焉尔。
举其大者为九。何其富也。夫九者。阳之盛数之极。故乾之策用九。而范有九畴。贡有九州。洞之有九曲。亦自然之数也。自夫朱夫子发武夷之奥。东人之占名区者。率多以九数焉。惟岭之陶山。海之石潭。尤著焉。岂惟地之胜欤。殆由人而显也。今牛耳之曲。如万景之雄奇。月影之清绝。未知孰与武夷。而即陶山石潭之所未有也。然其显不显。亦待乎人焉尔。牛耳墓山记
昔我曾王考判决事府君。以 肃庙庚寅下世。寿藏预卜于麻田地。至是多异议。将改卜近畿。醉村李相公。即府君长婿也。为言其先墓邻麓。多养山置标之地。盍试求诸。于是。遣地师。占得于牛耳洞天冠峰之东圭岩之下坐庚之原。遂奉襄焉。未几有毁之者。移窆于东麓矣。 英宗辛亥。曾王妣下世。将合封也。遇水患。复还奉于旧圹之下。见者咸称名穴。信乎物自有主也。当醉村公时。未及成券划送。故局内寸土一木。皆属于李氏。而守墓奴无所措手。不惟事势不便。抑恐后属渐远。或有争端。余于壬申。登科荣扫。仍往拜从祖姑贞敬夫人墓。于时醉村冢孙李相国溵。来住墓下。余为言山事。请归直而立券。李公曰。吾祖既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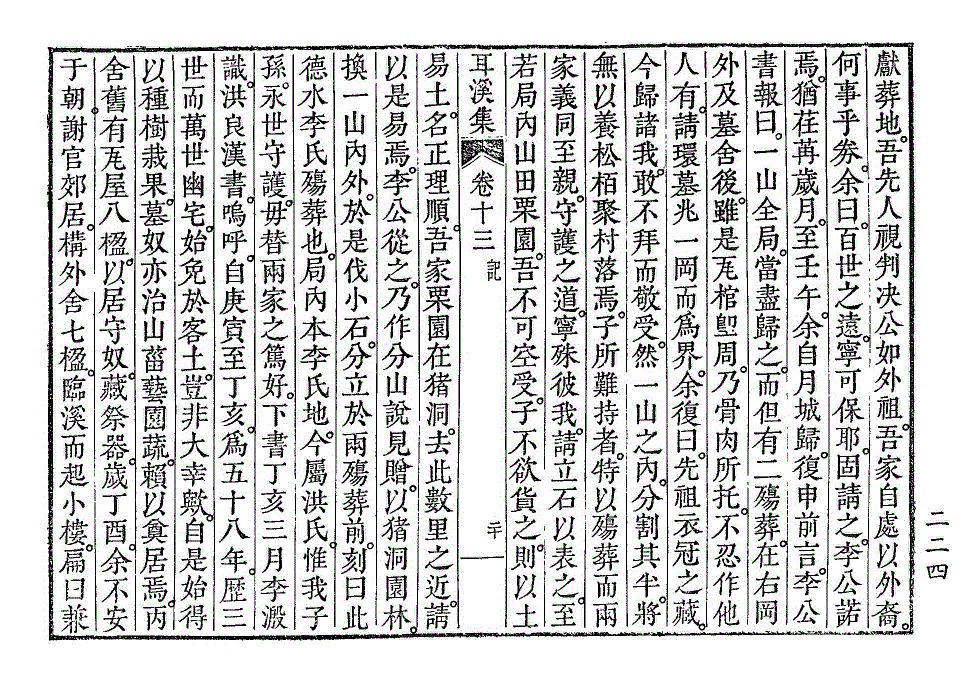 献葬地。吾先人视判决公如外祖。吾家自处以外裔。何事乎券。余曰。百世之远。宁可保耶。固请之。李公诺焉。犹荏苒岁月。至壬午。余自月城归。复申前言。李公书报曰。一山全局。当尽归之。而但有二殇葬。在右冈外及墓舍后。虽是瓦棺堲周。乃骨肉所托。不忍作他人有。请环墓兆一冈而为界。余复曰。先祖衣冠之藏。今归诸我。敢不拜而敬受。然一山之内。分割其半。将无以养松柏聚村落焉。子所难持者。特以殇葬而两家义同至亲。守护之道。宁殊彼我。请立石以表之。至若局内山田栗园。吾不可空受。子不欲货之。则以土易土。名正理顺。吾家栗园在猪洞。去此数里之近。请以是易焉。李公从之。乃作分山说见赠。以猪洞园林。换一山内外。于是伐小石。分立于两殇葬前。刻曰此德水李氏殇葬也。局内本李氏地。今属洪氏。惟我子孙。永世守护。毋替两家之笃好。下书丁亥三月李溵识。洪良汉书。呜呼。自庚寅至丁亥。为五十八年。历三世而万世幽宅。始免于客土。岂非大幸欤。自是始得以种树栽果。墓奴亦治山菑艺园蔬。赖以奠居焉。丙舍旧有瓦屋八楹。以居守奴。藏祭器。岁丁酉。余不安于朝。谢官郊居。构外舍七楹。临溪而起小楼。扁曰兼
献葬地。吾先人视判决公如外祖。吾家自处以外裔。何事乎券。余曰。百世之远。宁可保耶。固请之。李公诺焉。犹荏苒岁月。至壬午。余自月城归。复申前言。李公书报曰。一山全局。当尽归之。而但有二殇葬。在右冈外及墓舍后。虽是瓦棺堲周。乃骨肉所托。不忍作他人有。请环墓兆一冈而为界。余复曰。先祖衣冠之藏。今归诸我。敢不拜而敬受。然一山之内。分割其半。将无以养松柏聚村落焉。子所难持者。特以殇葬而两家义同至亲。守护之道。宁殊彼我。请立石以表之。至若局内山田栗园。吾不可空受。子不欲货之。则以土易土。名正理顺。吾家栗园在猪洞。去此数里之近。请以是易焉。李公从之。乃作分山说见赠。以猪洞园林。换一山内外。于是伐小石。分立于两殇葬前。刻曰此德水李氏殇葬也。局内本李氏地。今属洪氏。惟我子孙。永世守护。毋替两家之笃好。下书丁亥三月李溵识。洪良汉书。呜呼。自庚寅至丁亥。为五十八年。历三世而万世幽宅。始免于客土。岂非大幸欤。自是始得以种树栽果。墓奴亦治山菑艺园蔬。赖以奠居焉。丙舍旧有瓦屋八楹。以居守奴。藏祭器。岁丁酉。余不安于朝。谢官郊居。构外舍七楹。临溪而起小楼。扁曰兼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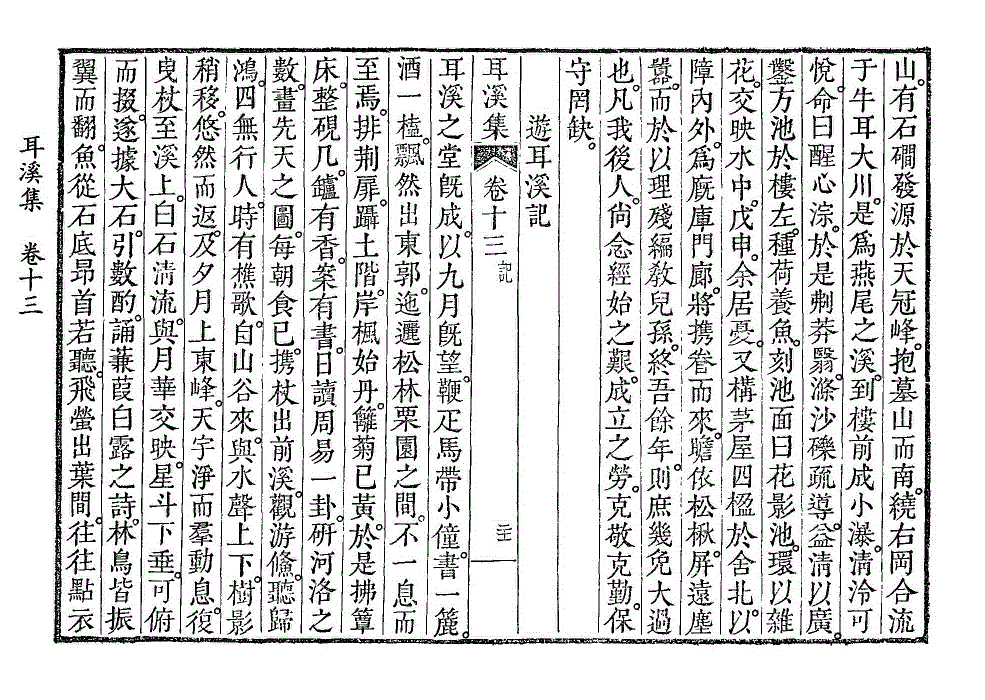 山。有石涧发源于天冠峰。抱墓山而南。绕右冈合流于牛耳大川。是为燕尾之溪。到楼前成小瀑。清泠可悦。命曰醒心淙。于是刜莽翳。涤沙砾疏导。益清以广。凿方池于楼左。种荷养鱼。刻池面曰花影池。环以杂花。交映水中。戊申。余居忧。又构茅屋四楹于舍北。以障内外。为厩库门廊。将携眷而来。瞻依松楸。屏远尘嚣。而于以理残编教儿孙。终吾馀年。则庶几免大过也。凡我后人。尚念经始之艰。成立之劳。克敬克勤。保守罔缺。
山。有石涧发源于天冠峰。抱墓山而南。绕右冈合流于牛耳大川。是为燕尾之溪。到楼前成小瀑。清泠可悦。命曰醒心淙。于是刜莽翳。涤沙砾疏导。益清以广。凿方池于楼左。种荷养鱼。刻池面曰花影池。环以杂花。交映水中。戊申。余居忧。又构茅屋四楹于舍北。以障内外。为厩库门廊。将携眷而来。瞻依松楸。屏远尘嚣。而于以理残编教儿孙。终吾馀年。则庶几免大过也。凡我后人。尚念经始之艰。成立之劳。克敬克勤。保守罔缺。游耳溪记
耳溪之堂既成。以九月既望。鞭疋马带小僮。书一簏。酒一榼。飘然出东郭。迤逦松林栗园之间。不一息而至焉。排荆扉。蹑土阶。岸枫始丹。篱菊已黄。于是拂簟床。整砚几。垆有香。案有书。日读周易一卦。研河洛之数。画先天之图。每朝食已。携杖出前溪。观游鯈。听归鸿。四无行人。时有樵歌。自山谷来。与水声上下。树影稍移。悠然而返。及夕月上东峰。天宇净而群动息。复曳杖至溪上。白石清流。与月华交映。星斗下垂。可俯而掇。遂据大石。引数酌。诵蒹葭白露之诗。林鸟皆振翼而翻。鱼从石底昂首若听。飞萤出叶间。往往点衣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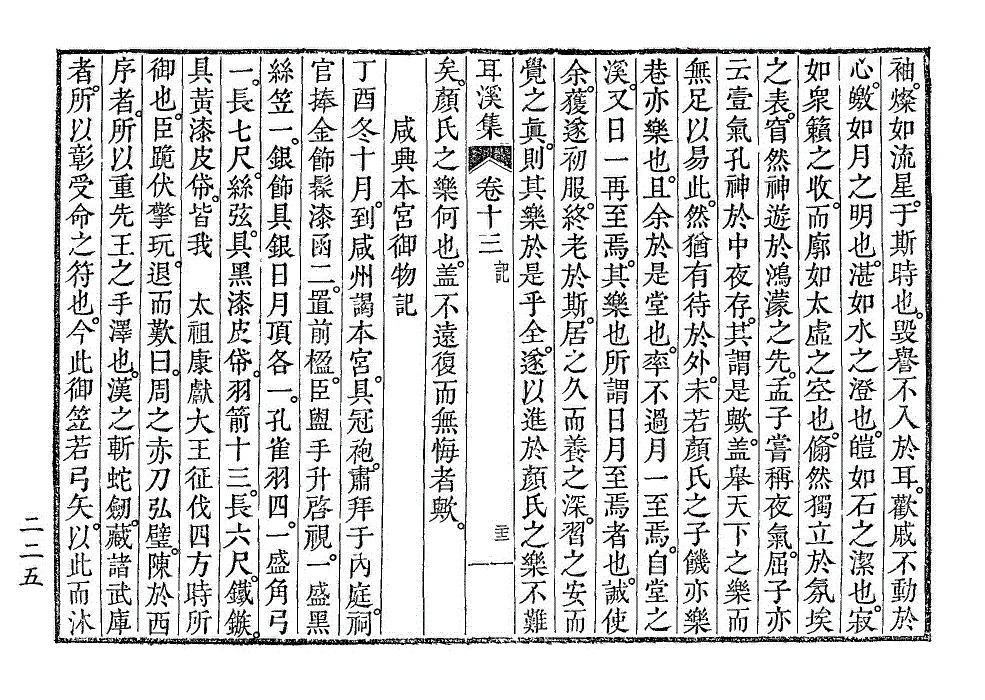 袖。灿如流星。于斯时也。毁誉不入于耳。欢戚不动于心。皦如月之明也。湛如水之澄也。皑如石之洁也。寂如众籁之收。而廓如太虚之空也。翛然独立于氛埃之表。窅然神游于鸿濛之先。孟子尝称夜气。屈子亦云壹气孔神于中夜存。其谓是欤。盖举天下之乐而无足以易此。然犹有待于外。未若颜氏之子饥亦乐巷亦乐也。且余于是堂也。率不过月一至焉。自堂之溪。又日一再至焉。其乐也所谓日月至焉者也。诚使余。获遂初服。终老于斯。居之久而养之深。习之安而觉之真。则其乐于是乎全。遂以进于颜氏之乐不难矣。颜氏之乐何也。盖不远复而无悔者欤。
袖。灿如流星。于斯时也。毁誉不入于耳。欢戚不动于心。皦如月之明也。湛如水之澄也。皑如石之洁也。寂如众籁之收。而廓如太虚之空也。翛然独立于氛埃之表。窅然神游于鸿濛之先。孟子尝称夜气。屈子亦云壹气孔神于中夜存。其谓是欤。盖举天下之乐而无足以易此。然犹有待于外。未若颜氏之子饥亦乐巷亦乐也。且余于是堂也。率不过月一至焉。自堂之溪。又日一再至焉。其乐也所谓日月至焉者也。诚使余。获遂初服。终老于斯。居之久而养之深。习之安而觉之真。则其乐于是乎全。遂以进于颜氏之乐不难矣。颜氏之乐何也。盖不远复而无悔者欤。咸兴本宫御物记
丁酉冬十月。到咸州谒本宫。具冠袍。肃拜于内庭。祠官捧金饰髹漆函二。置前楹。臣盥手升启视。一盛黑丝笠一。银饰具银日月顶各一。孔雀羽四。一盛角弓一。长七尺。丝弦。具黑漆皮袋。羽箭十三。长六尺。铁镞。具黄漆皮袋。皆我 太祖康献大王征伐四方时所御也。臣跪伏擎玩。退而叹曰。周之赤刀弘璧。陈于西序者。所以重先王之手泽也。汉之斩蛇剑。藏诸武库者。所以彰受命之符也。今此御笠若弓矢。以此而沐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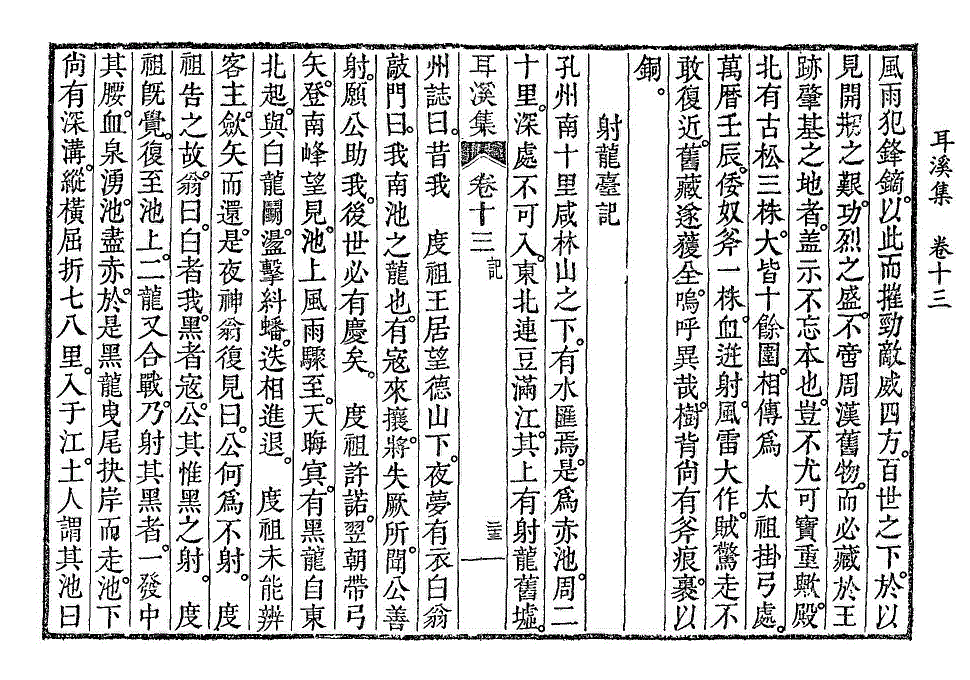 风雨犯锋镝。以此而摧劲敌威四方。百世之下。于以见开刱之艰。功烈之盛。不啻周汉旧物。而必藏于王迹肇基之地者。盖示不忘本也。岂不尤可宝重欤。殿北有古松三株。大皆十馀围。相传为 太祖挂弓处。万历壬辰。倭奴斧一株。血迸射。风雷大作。贼惊走不敢复近。旧藏遂获全。呜呼异哉。树背尚有斧痕。裹以铜。
风雨犯锋镝。以此而摧劲敌威四方。百世之下。于以见开刱之艰。功烈之盛。不啻周汉旧物。而必藏于王迹肇基之地者。盖示不忘本也。岂不尤可宝重欤。殿北有古松三株。大皆十馀围。相传为 太祖挂弓处。万历壬辰。倭奴斧一株。血迸射。风雷大作。贼惊走不敢复近。旧藏遂获全。呜呼异哉。树背尚有斧痕。裹以铜。射龙台记
孔州南十里咸林山之下。有水汇焉。是为赤池。周二十里。深处不可入。东北连豆满江。其上有射龙旧墟。州志曰。昔我 度祖王居望德山下。夜梦有衣白翁敲门曰。我南池之龙也。有寇来攘。将失厥所。闻公善射。愿公助我。后世必有庆矣。 度祖许诺。翌朝带弓矢。登南峰望见。池上风雨骤至。天晦冥。有黑龙自东北起。与白龙斗。荡击纠蟠。迭相进退。 度祖未能辨客主。敛矢而还。是夜神翁复见曰。公何为不射。 度祖告之故。翁曰。白者我。黑者寇。公其惟黑之射。 度祖既觉。复至池上。二龙又合战。乃射其黑者。一发中其腰。血泉涌。池尽赤。于是黑龙曳尾抉岸而走。池下尚有深沟。纵横屈折七八里。入于江。土人谓其池曰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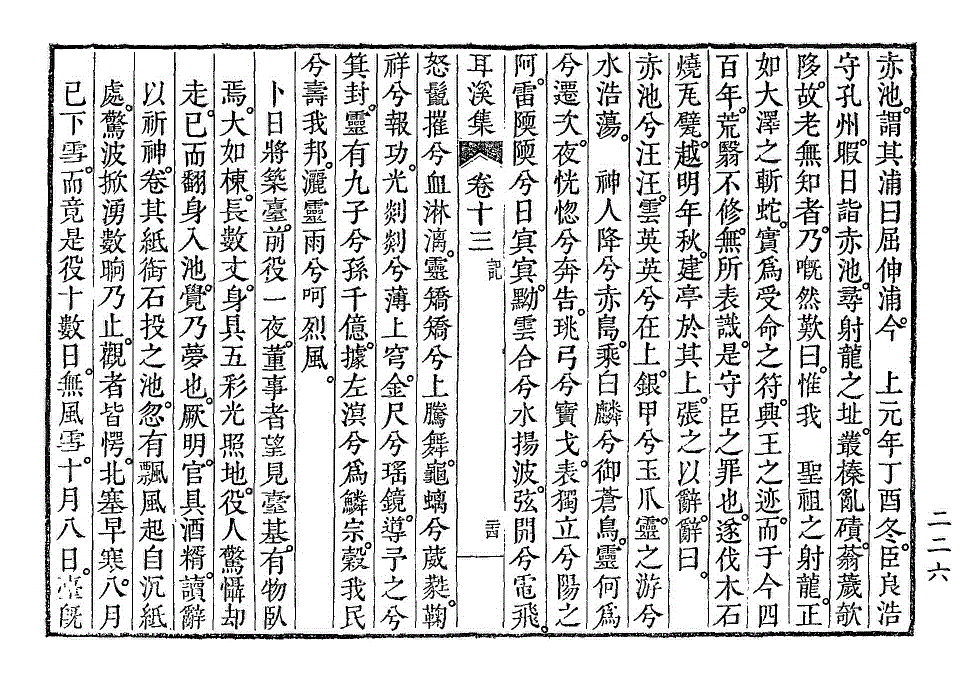 赤池。谓其浦曰屈伸浦。今 上元年丁酉冬。臣良浩守孔州。暇日诣赤池。寻射龙之址。丛榛乱碛。蓊秽欹陊。故老无知者。乃嘅然叹曰。惟我 圣祖之射龙。正如大泽之斩蛇。实为受命之符。兴王之迹。而于今四百年。荒翳不修。无所表识。是守臣之罪也。遂伐木石烧瓦甓。越明年秋。建亭于其上。张之以辞。辞曰。
赤池。谓其浦曰屈伸浦。今 上元年丁酉冬。臣良浩守孔州。暇日诣赤池。寻射龙之址。丛榛乱碛。蓊秽欹陊。故老无知者。乃嘅然叹曰。惟我 圣祖之射龙。正如大泽之斩蛇。实为受命之符。兴王之迹。而于今四百年。荒翳不修。无所表识。是守臣之罪也。遂伐木石烧瓦甓。越明年秋。建亭于其上。张之以辞。辞曰。赤池兮汪汪。云英英兮在上。银甲兮玉爪。灵之游兮水浩荡。 神人降兮赤岛。乘白麟兮御苍鸟。灵何为兮迁次。夜恍惚兮奔告。珧弓兮宝戈。表独立兮阳之阿。雷陾陾兮日冥冥。黝云合兮水扬波。弦开兮电飞。怒鬣摧兮血淋漓。灵矫矫兮上腾舞。龟螭兮葳蕤。鞠祥兮报功。光剡剡兮薄上穹。金尺兮瑶镜。导予之兮箕封。灵有九子兮孙千亿。据左溟兮为鳞宗。谷我民兮寿我邦。洒灵雨兮呵烈风。
卜日将筑台。前役一夜。董事者望见台基。有物卧焉。大如栋。长数丈。身具五彩光照地。役人惊慑却走。已而翻身入池。觉乃梦也。厥明。官具酒糈。读辞以祈神。卷其纸衔石投之池。忽有飘风起自沉纸处。惊波掀涌数晌乃止。观者皆愕。北塞早寒。八月已下雪。而竟是役十数日。无风雪。十月八日。台既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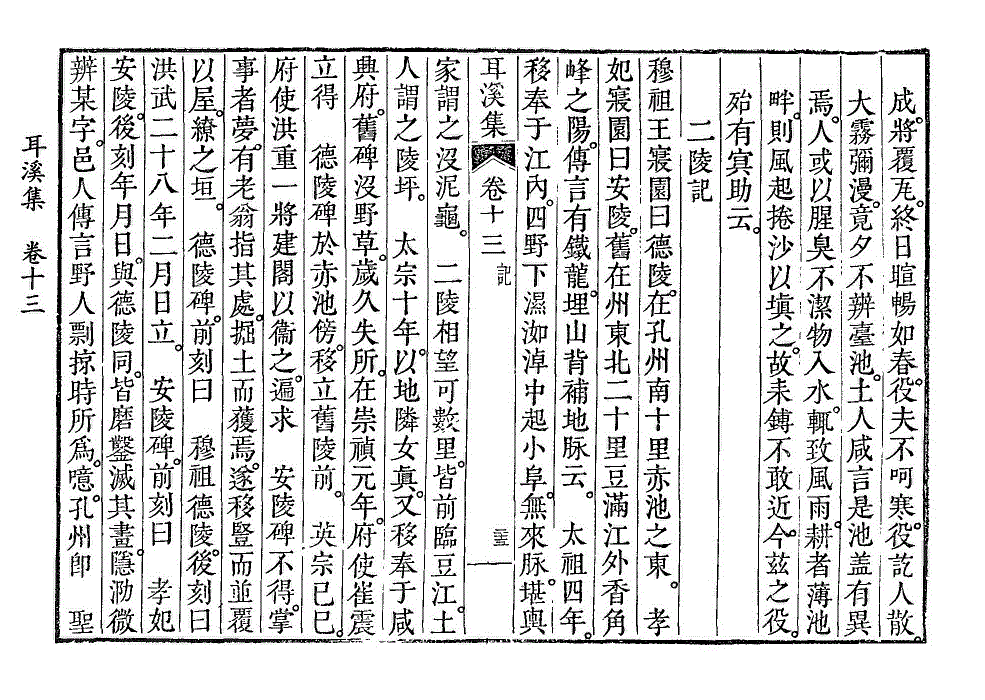 成。将覆瓦。终日暄畅如春。役夫不呵寒。役讫人散。大雾弥漫。竟夕不辨台池。土人咸言是池盖有异焉。人或以腥臭不洁物入水。辄致风雨。耕者薄池畔。则风起捲沙以填之。故耒镈不敢近。今玆之役。殆有冥助云。
成。将覆瓦。终日暄畅如春。役夫不呵寒。役讫人散。大雾弥漫。竟夕不辨台池。土人咸言是池盖有异焉。人或以腥臭不洁物入水。辄致风雨。耕者薄池畔。则风起捲沙以填之。故耒镈不敢近。今玆之役。殆有冥助云。二陵记
穆祖王寝园曰德陵。在孔州南十里赤池之东。 孝妃寝园曰安陵。旧在州东北二十里豆满江外香角峰之阳。传言有铁龙。埋山背补地脉云。 太祖四年。移奉于江内。四野下湿洳淖中起小阜。无来脉。堪舆家谓之没泥龟。 二陵相望可数里。皆前临豆江。土人谓之陵坪。 太宗十年。以地邻女真。又移奉于咸兴府。旧碑没野草。岁久失所。在崇祯元年。府使崔震立得 德陵碑于赤池傍。移立旧陵前。 英宗己巳。府使洪重一将建阁以卫之。遍求 安陵碑不得。掌事者梦。有老翁指其处。掘土而获焉。遂移竖而并覆以屋。缭之垣。 德陵碑。前刻曰 穆祖德陵。后刻曰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立。 安陵碑。前刻曰 孝妃安陵。后刻年月日。与德陵同。皆磨凿灭其画。隐泐微辨某字。邑人传言野人剽掠时所为。噫。孔州即 圣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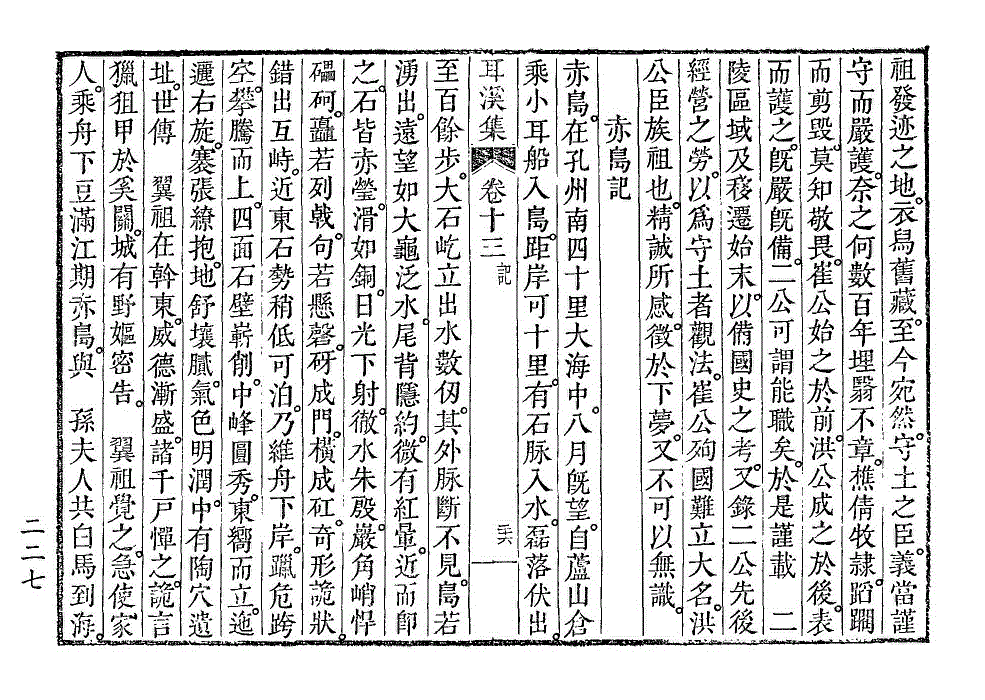 祖发迹之地。衣舄旧藏。至今宛然。守土之臣。义当谨守而严护。奈之何数百年埋翳不章。樵倩牧隶。蹈躏而剪毁。莫知敬畏。崔公始之于前。洪公成之于后。表而护之。既严既备。二公可谓能职矣。于是谨载 二陵区域及移迁始末。以备国史之考。又录二公先后经营之劳。以为守土者观法。崔公殉国难立大名。洪公臣族祖也。精诚所感。徵于下梦。又不可以无识。
祖发迹之地。衣舄旧藏。至今宛然。守土之臣。义当谨守而严护。奈之何数百年埋翳不章。樵倩牧隶。蹈躏而剪毁。莫知敬畏。崔公始之于前。洪公成之于后。表而护之。既严既备。二公可谓能职矣。于是谨载 二陵区域及移迁始末。以备国史之考。又录二公先后经营之劳。以为守土者观法。崔公殉国难立大名。洪公臣族祖也。精诚所感。徵于下梦。又不可以无识。赤岛记
赤岛。在孔州南四十里大海中。八月既望。自芦山仓乘小耳船入岛。距岸可十里。有石脉入水。磊落伏出。至百馀步。大石屹立出水数仞。其外脉断不见。岛若涌出。远望如大龟泛水。尾背隐约。微有红晕。近而即之。石皆赤莹。滑如铜。日光下射。彻水朱殷。岩角峭悍礧砢。矗若列戟。句若悬磬。砑成门。横成矼。奇形诡状。错出互峙。近东石势稍低可泊。乃维舟下岸。躐危跨空。攀腾而上。四面石壁崭削。中峰圆秀。东向而立。迤逦右旋。褰张缭抱。地舒壤腻。气色明润。中有陶穴遗址。世传 翼祖在斡东。威德渐盛。诸千户惮之。诡言猎狙甲于奚关。城有野妪密告。 翼祖觉之。急使家人。乘舟下豆满江期赤岛。与 孙夫人共白马到海。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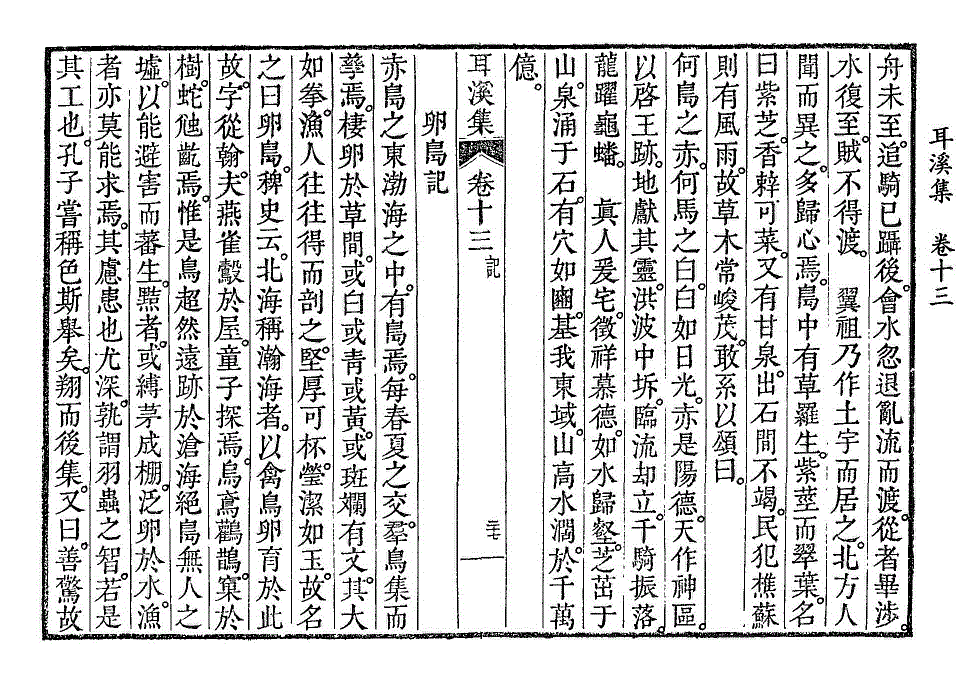 舟未至。追骑已蹑后。会水忽退乱流而渡。从者毕涉。水复至。贼不得渡。 翼祖乃作土宇而居之。北方人闻而异之。多归心焉。岛中有草罗生。紫茎而翠叶。名曰紫芝。香辣可菜。又有甘泉。出石间不竭。民犯樵苏则有风雨。故草木常峻茂。敢系以颂曰。
舟未至。追骑已蹑后。会水忽退乱流而渡。从者毕涉。水复至。贼不得渡。 翼祖乃作土宇而居之。北方人闻而异之。多归心焉。岛中有草罗生。紫茎而翠叶。名曰紫芝。香辣可菜。又有甘泉。出石间不竭。民犯樵苏则有风雨。故草木常峻茂。敢系以颂曰。何岛之赤。何马之白。白如日光。赤是阳德。天作神区。以启王迹。地献其灵。洪波中坼。临流却立。千骑振落。龙跃龟蟠。 真人爰宅。徵祥慕德。如水归壑。芝茁于山。泉涌于石。有穴如豳。基我东域。山高水阔。于千万亿。
卵岛记
赤岛之东渤海之中。有岛焉。每春夏之交。群鸟集而孳焉。栖卵于草间。或白或青或黄。或斑斓有文。其大如拳。渔人往往得而剖之。坚厚可杯。莹洁如玉。故名之曰卵岛。稗史云。北海称瀚海者。以禽鸟卵育于此故。字从翰。夫燕雀鷇于屋。童子探焉。乌鸢鹳鹊。窠于树。蛇虺龁焉。惟是鸟超然远迹于沧海绝岛无人之墟。以能避害而蕃生。黠者。或缚茅成棚。泛卵于水。渔者亦莫能求焉。其虑患也尤深。孰谓羽虫之智。若是其工也。孔子尝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又曰。善惊故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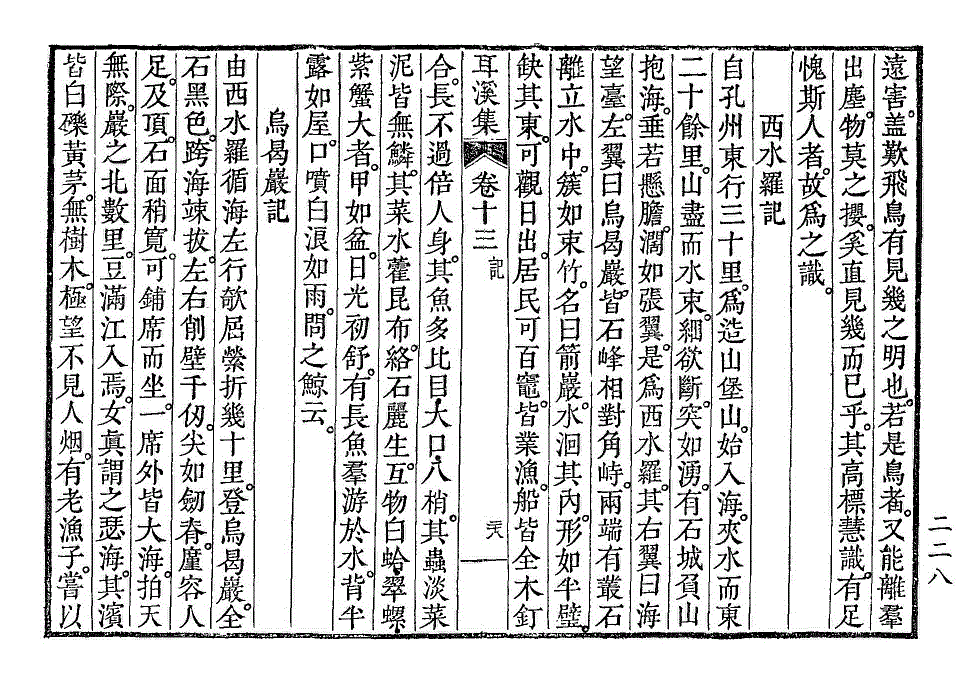 远害。盖叹飞鸟有见几之明也。若是鸟者。又能离群出尘。物莫之撄。奚直见几而已乎。其高标慧识。有足愧斯人者。故为之识。
远害。盖叹飞鸟有见几之明也。若是鸟者。又能离群出尘。物莫之撄。奚直见几而已乎。其高标慧识。有足愧斯人者。故为之识。西水罗记
自孔州东行三十里。为造山堡山。始入海。夹水而东二十馀里。山尽而水束。细欲断。突如涌。有石城负山抱海。垂若悬胆。阔如张翼。是为西水罗。其右翼曰海望台。左翼曰乌曷岩。皆石峰相对角峙。两端有丛石离立水中。簇如束竹。名曰箭岩。水洄其内。形如半璧。缺其东。可观日出。居民可百灶。皆业渔。船皆全木钉合。长不过倍人身。其鱼多比目,大口,八梢。其虫淡菜泥皆无鳞。其菜水藿昆布。络石丽生。互物白蛤,翠螺,紫蟹大者。甲如盆。日光初舒。有长鱼群游于水。背半露如屋。口喷白浪如雨。问之鲸云。
乌曷岩记
由西水罗循海左行欹屈萦折几十里。登乌曷岩。全石黑色。跨海竦拔。左右削壁千仞。尖如剑脊。廑容人足。及顶。石面稍宽。可铺席而坐。一席外皆大海。拍天无际。岩之北数里。豆满江入焉。女真谓之瑟海。其滨皆白砾黄茅。无树木。极望不见人烟。有老渔子。尝以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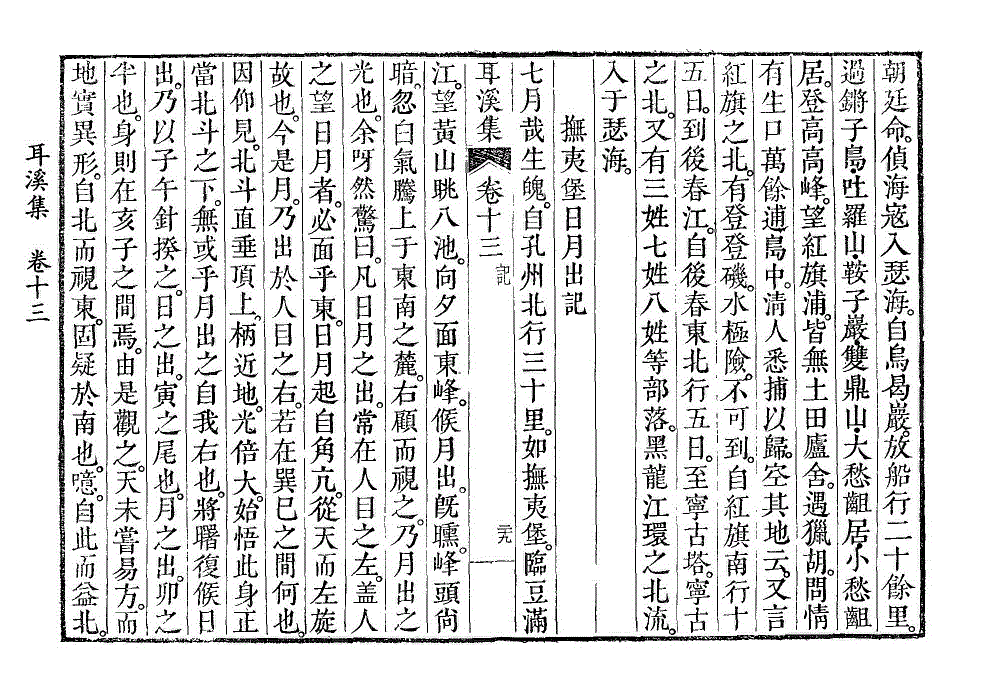 朝廷命。侦海寇入瑟海。自乌曷岩。放船行二十馀里。过锵子岛,吐罗山,鞍子岩,双鼎山,大愁龃居,小愁龃居。登高高峰。望红旗浦。皆无土田庐舍。遇猎胡。问情有生口万馀逋岛中。清人悉捕以归。空其地云。又言红旗之北。有登登矶。水极险。不可到。自红旗南行十五日。到后春江。自后春东北行五日。至宁古塔。宁古之北。又有三姓七姓八姓等部落。黑龙江环之北流。入于瑟海。
朝廷命。侦海寇入瑟海。自乌曷岩。放船行二十馀里。过锵子岛,吐罗山,鞍子岩,双鼎山,大愁龃居,小愁龃居。登高高峰。望红旗浦。皆无土田庐舍。遇猎胡。问情有生口万馀逋岛中。清人悉捕以归。空其地云。又言红旗之北。有登登矶。水极险。不可到。自红旗南行十五日。到后春江。自后春东北行五日。至宁古塔。宁古之北。又有三姓七姓八姓等部落。黑龙江环之北流。入于瑟海。抚夷堡日月出记
七月哉生魄。自孔州北行三十里。如抚夷堡。临豆满江。望黄山眺八池。向夕面东峰。候月出。既曛。峰头尚暗。忽白气腾上于东南之麓。右顾而视之。乃月出之光也。余呀然惊曰。凡日月之出。常在人目之左。盖人之望日月者。必面乎东。日月起自角亢。从天而左旋故也。今是月。乃出于人目之右。若在巽巳之间何也。因仰见。北斗直垂顶上。柄近地。光倍大。始悟此身正当北斗之下。无或乎月出之自我右也。将曙复候日出。乃以子午针揆之。日之出。寅之尾也。月之出。卯之半也。身则在亥子之间焉。由是观之。天未尝易方。而地实异形。自北而视东。固疑于南也。噫。自此而益北。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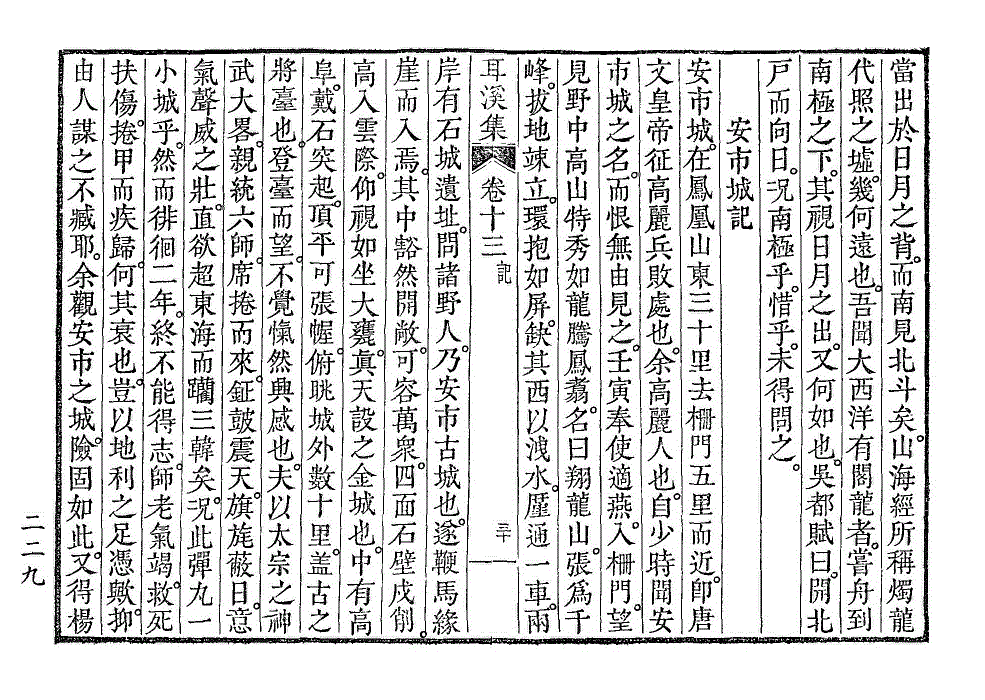 当出于日月之背。而南见北斗矣。山海经所称烛龙代照之墟。几何远也。吾闻大西洋有阁龙者。尝舟到南极之下。其视日月之出。又何如也。吴都赋曰。开北户而向日。况南极乎。惜乎。未得问之。
当出于日月之背。而南见北斗矣。山海经所称烛龙代照之墟。几何远也。吾闻大西洋有阁龙者。尝舟到南极之下。其视日月之出。又何如也。吴都赋曰。开北户而向日。况南极乎。惜乎。未得问之。安市城记
安市城。在凤凰山东三十里去栅门五里而近。即唐文皇帝征高丽兵败处也。余高丽人也。自少时闻安市城之名。而恨无由见之。壬寅奉使适燕。入栅门。望见野中高山特秀如龙腾凤翥。名曰翔龙山。张为千峰。拔地竦立。环抱如屏。缺其西以泄水。廑通一车。两岸有石城遗址。问诸野人。乃安市古城也。遂鞭马缘崖而入焉。其中豁然开敞。可容万众。四面石壁戍削。高入云际。仰视如坐大瓮。真天设之金城也。中有高阜。戴石突起。顶平可张幄。俯眺城外数十里。盖古之将台也。登台而望。不觉忾然兴感也。夫以太宗之神武大略。亲统六师。席捲而来。钲鼓震天。旗旄蔽日。意气声威之壮。直欲超东海而躏三韩矣。况此弹丸一小城乎。然而徘徊二年。终不能得志。师老气竭。救死扶伤。捲甲而疾归。何其衰也。岂以地利之足凭欤。抑由人谋之不臧耶。余观安市之城。险固如此。又得杨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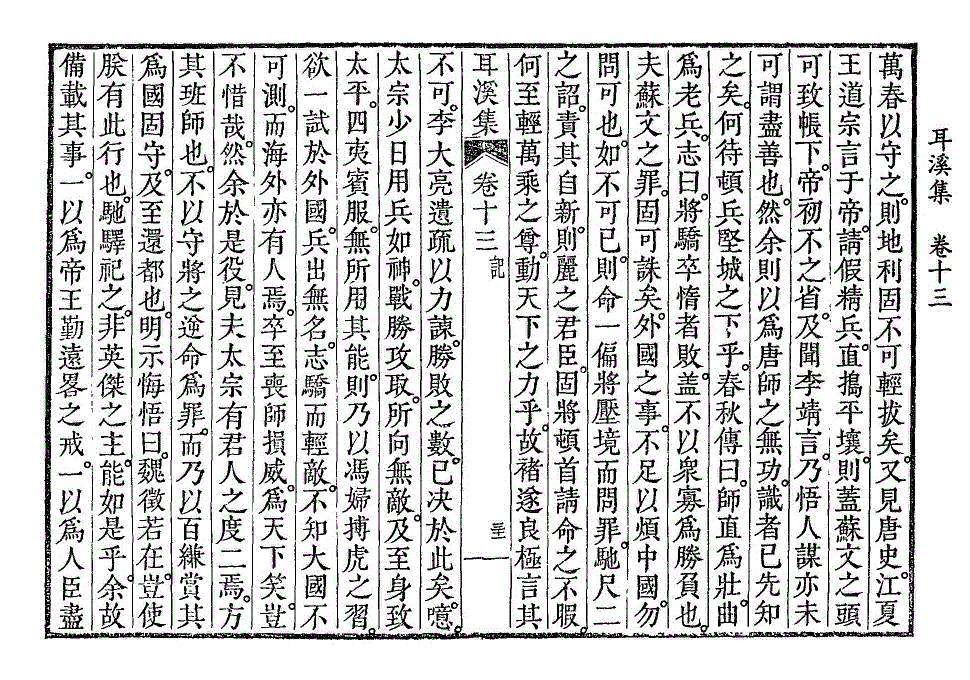 万春以守之。则地利固不可轻拔矣。又见唐史。江夏王道宗言于帝。请假精兵。直捣平壤。则盖苏文之头可致帐下。帝初不之省。及闻李靖言。乃悟人谋亦未可谓尽善也。然余则以为唐师之无功。识者已先知之矣。何待顿兵坚城之下乎。春秋传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兵。志曰。将骄卒惰者败。盖不以众寡为胜负也。夫苏文之罪。固可诛矣。外国之事。不足以烦中国。勿问可也。如不可已。则命一偏将压境而问罪。驰尺二之诏。责其自新。则丽之君臣。固将顿首请命之不暇。何至轻万乘之尊。动天下之力乎。故褚遂良极言其不可。李大亮遗疏以力谏。胜败之数。已决于此矣。噫。太宗少日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所向无敌。及至身致太平。四夷宾服。无所用其能。则乃以冯妇搏虎之习。欲一试于外国。兵出无名。志骄而轻敌。不知大国不可测。而海外亦有人焉。卒至丧师损威。为天下笑。岂不惜哉。然余于是役。见夫太宗有君人之度二焉。方其班师也。不以守将之逆命为罪。而乃以百缣赏其为国固守。及至还都也。明示悔悟曰。魏徵若在。岂使朕有此行也。驰驿祀之。非英杰之主。能如是乎。余故备载其事。一以为帝王勤远略之戒。一以为人臣尽
万春以守之。则地利固不可轻拔矣。又见唐史。江夏王道宗言于帝。请假精兵。直捣平壤。则盖苏文之头可致帐下。帝初不之省。及闻李靖言。乃悟人谋亦未可谓尽善也。然余则以为唐师之无功。识者已先知之矣。何待顿兵坚城之下乎。春秋传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兵。志曰。将骄卒惰者败。盖不以众寡为胜负也。夫苏文之罪。固可诛矣。外国之事。不足以烦中国。勿问可也。如不可已。则命一偏将压境而问罪。驰尺二之诏。责其自新。则丽之君臣。固将顿首请命之不暇。何至轻万乘之尊。动天下之力乎。故褚遂良极言其不可。李大亮遗疏以力谏。胜败之数。已决于此矣。噫。太宗少日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所向无敌。及至身致太平。四夷宾服。无所用其能。则乃以冯妇搏虎之习。欲一试于外国。兵出无名。志骄而轻敌。不知大国不可测。而海外亦有人焉。卒至丧师损威。为天下笑。岂不惜哉。然余于是役。见夫太宗有君人之度二焉。方其班师也。不以守将之逆命为罪。而乃以百缣赏其为国固守。及至还都也。明示悔悟曰。魏徵若在。岂使朕有此行也。驰驿祀之。非英杰之主。能如是乎。余故备载其事。一以为帝王勤远略之戒。一以为人臣尽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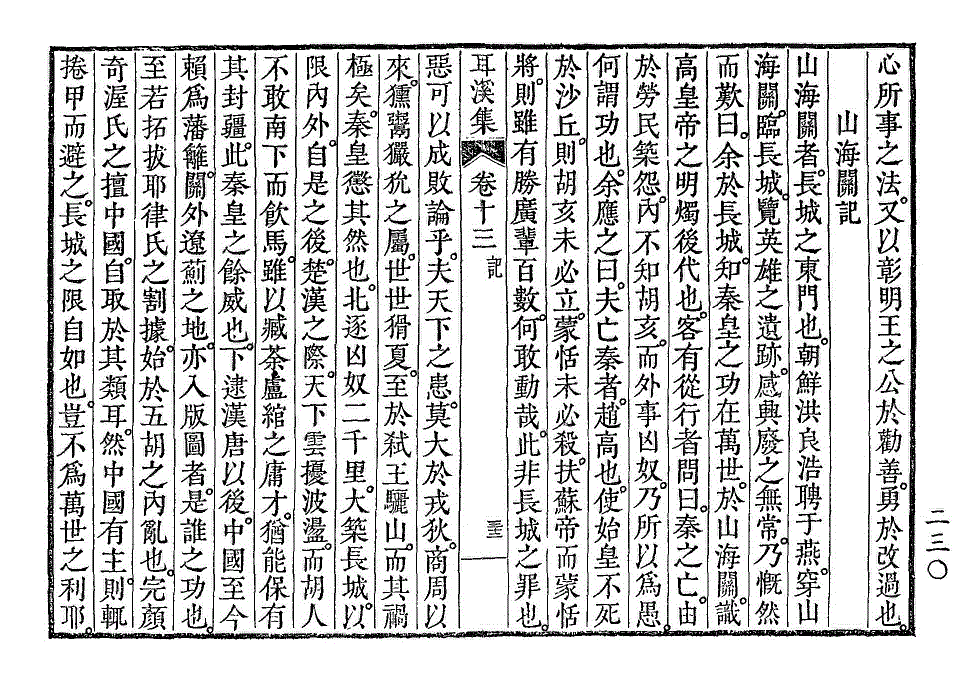 心所事之法。又以彰明王之公于劝善。勇于改过也。
心所事之法。又以彰明王之公于劝善。勇于改过也。山海关记
山海关者。长城之东门也。朝鲜洪良浩聘于燕。穿山海关。临长城。览英雄之遗迹。感兴废之无常。乃慨然而叹曰。余于长城。知秦皇之功在万世。于山海关。识高皇帝之明烛后代也。客有从行者问曰。秦之亡。由于劳民筑怨。内不知胡亥。而外事凶奴。乃所以为愚。何谓功也。余应之曰。夫亡秦者。赵高也。使始皇不死于沙丘。则胡亥未必立。蒙恬未必杀。扶苏帝而蒙恬将。则虽有胜,广辈百数。何敢动哉。此非长城之罪也。恶可以成败论乎。夫天下之患。莫大于戎狄。商周以来。獯鬻猃狁之属。世世猾夏。至于弑王骊山。而其祸极矣。秦皇惩其然也。北逐凶奴二千里。大筑长城。以限内外。自是之后。楚汉之际。天下云扰波荡。而胡人不敢南下而饮马。虽以臧荼,卢绾之庸才。犹能保有其封疆。此秦皇之馀威也。下逮汉唐以后。中国至今赖为藩篱。关外辽蓟之地。亦入版图者。是谁之功也。至若拓拔耶律氏之割据。始于五胡之内乱也。完颜奇渥氏之擅中国。自取于其类耳。然中国有主。则辄捲甲而避之。长城之限自如也。岂不为万世之利耶。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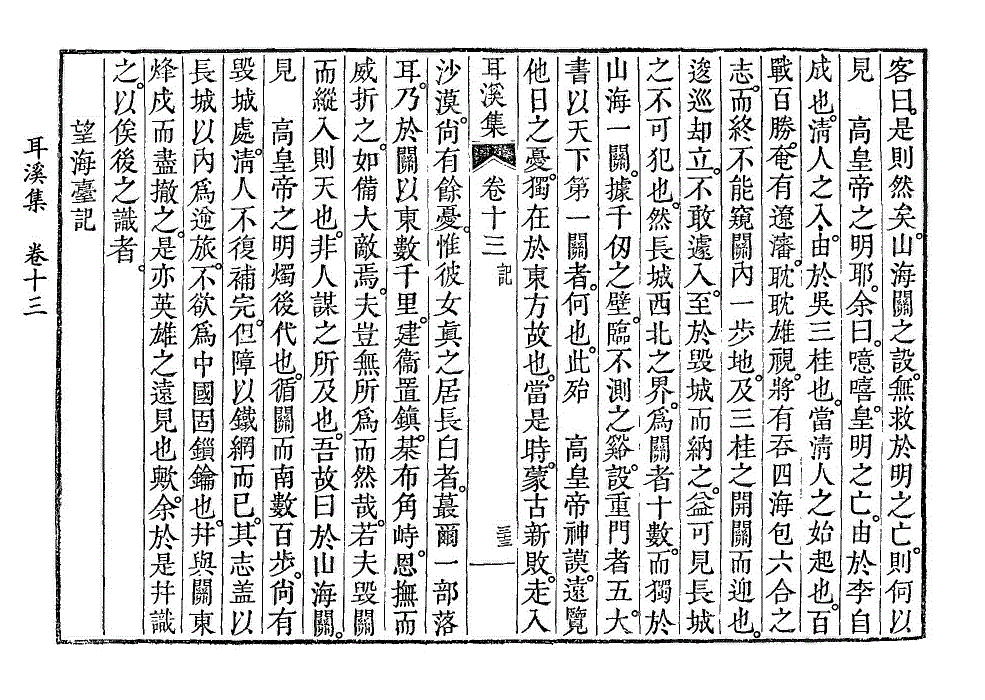 客曰。是则然矣。山海关之设。无救于明之亡。则何以见 高皇帝之明耶。余曰。噫嘻。皇明之亡。由于李自成也。清人之入。由于吴三桂也。当清人之始起也。百战百胜。奄有辽沈。耽耽雄视。将有吞四海包六合之志。而终不能窥关内一步地。及三桂之开关而迎也。逡巡却立。不敢遽入。至于毁城而纳之。益可见长城之不可犯也。然长城西北之界。为关者十数。而独于山海一关。据千仞之壁。临不测之溪。设重门者五。大书以天下第一关者。何也。此殆 高皇帝神谟。远览他日之忧。独在于东方故也。当是时。蒙古新败。走入沙漠。尚有馀忧。惟彼女真之居长白者。蕞尔一部落耳。乃于关以东数千里。建卫置镇。棋布角峙。恩抚而威折之。如备大敌焉。夫岂无所为而然哉。若夫毁关而纵入则天也。非人谋之所及也。吾故曰于山海关。见 高皇帝之明烛后代也。循关而南数百步。尚有毁城处。清人不复补完。但障以铁网而已。其志盖以长城以内为逆旅。不欲为中国固锁钥也。并与关东烽戍而尽撤之。是亦英雄之远见也欤。余于是并识之。以俟后之识者。
客曰。是则然矣。山海关之设。无救于明之亡。则何以见 高皇帝之明耶。余曰。噫嘻。皇明之亡。由于李自成也。清人之入。由于吴三桂也。当清人之始起也。百战百胜。奄有辽沈。耽耽雄视。将有吞四海包六合之志。而终不能窥关内一步地。及三桂之开关而迎也。逡巡却立。不敢遽入。至于毁城而纳之。益可见长城之不可犯也。然长城西北之界。为关者十数。而独于山海一关。据千仞之壁。临不测之溪。设重门者五。大书以天下第一关者。何也。此殆 高皇帝神谟。远览他日之忧。独在于东方故也。当是时。蒙古新败。走入沙漠。尚有馀忧。惟彼女真之居长白者。蕞尔一部落耳。乃于关以东数千里。建卫置镇。棋布角峙。恩抚而威折之。如备大敌焉。夫岂无所为而然哉。若夫毁关而纵入则天也。非人谋之所及也。吾故曰于山海关。见 高皇帝之明烛后代也。循关而南数百步。尚有毁城处。清人不复补完。但障以铁网而已。其志盖以长城以内为逆旅。不欲为中国固锁钥也。并与关东烽戍而尽撤之。是亦英雄之远见也欤。余于是并识之。以俟后之识者。望海台记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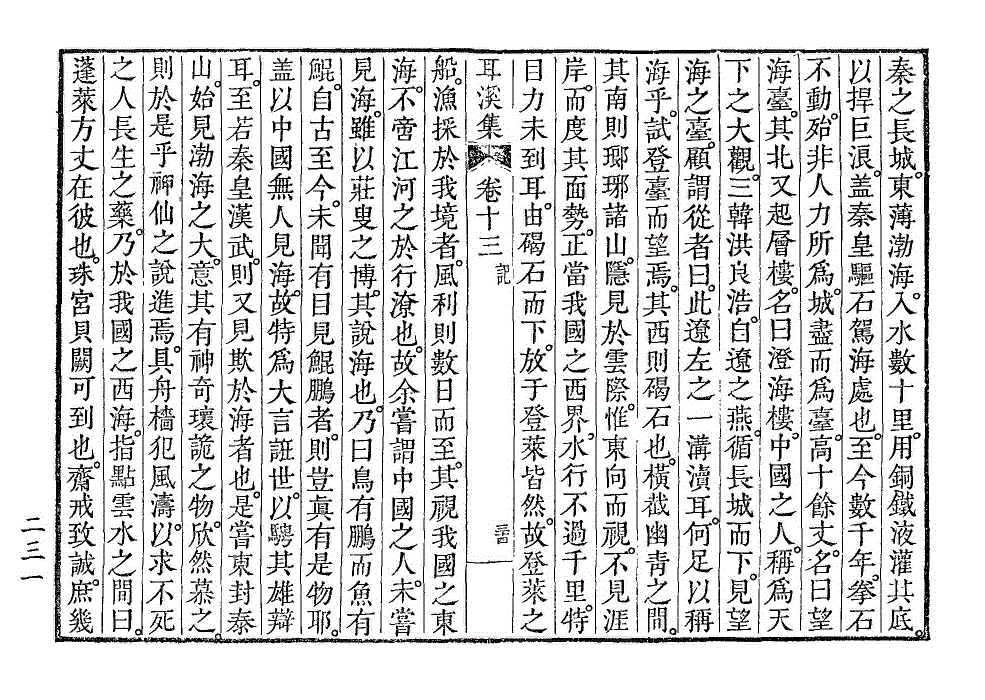 秦之长城。东薄渤海。入水数十里。用铜铁液灌其底。以捍巨浪。盖秦皇驱石驾海处也。至今数千年。拳石不动。殆非人力所为。城尽而为台。高十馀丈。名曰望海台。其北又起层楼。名曰澄海楼。中国之人。称为天下之大观。三韩洪良浩。自辽之燕。循长城而下。见望海之台。顾谓从者曰。此辽左之一沟渎耳。何足以称海乎。试登台而望焉。其西则碣石也。横截幽青之间。其南则琅琊诸山。隐见于云际。惟东向而视。不见涯岸。而度其面势。正当我国之西界。水行不过千里。特目力未到耳。由碣石而下。放于登莱皆然。故登莱之船。渔采于我境者。风利则数日而至。其视我国之东海。不啻江河之于行潦也。故余尝谓中国之人。未尝见海。虽以庄叟之博。其说海也。乃曰鸟有鹏而鱼有鲲。自古至今。未闻有目见鲲鹏者。则岂真有是物耶。盖以中国无人见海。故特为大言诳世。以骋其雄辩耳。至若秦皇汉武。则又见欺于海者也。是尝东封泰山。始见渤海之大。意其有神奇瑰诡之物。欣然慕之。则于是乎神仙之说进焉。具舟樯犯风涛。以求不死之人长生之药。乃于我国之西海。指点云水之间曰。蓬莱方丈在彼也。珠宫贝阙可到也。斋戒致诚。庶几
秦之长城。东薄渤海。入水数十里。用铜铁液灌其底。以捍巨浪。盖秦皇驱石驾海处也。至今数千年。拳石不动。殆非人力所为。城尽而为台。高十馀丈。名曰望海台。其北又起层楼。名曰澄海楼。中国之人。称为天下之大观。三韩洪良浩。自辽之燕。循长城而下。见望海之台。顾谓从者曰。此辽左之一沟渎耳。何足以称海乎。试登台而望焉。其西则碣石也。横截幽青之间。其南则琅琊诸山。隐见于云际。惟东向而视。不见涯岸。而度其面势。正当我国之西界。水行不过千里。特目力未到耳。由碣石而下。放于登莱皆然。故登莱之船。渔采于我境者。风利则数日而至。其视我国之东海。不啻江河之于行潦也。故余尝谓中国之人。未尝见海。虽以庄叟之博。其说海也。乃曰鸟有鹏而鱼有鲲。自古至今。未闻有目见鲲鹏者。则岂真有是物耶。盖以中国无人见海。故特为大言诳世。以骋其雄辩耳。至若秦皇汉武。则又见欺于海者也。是尝东封泰山。始见渤海之大。意其有神奇瑰诡之物。欣然慕之。则于是乎神仙之说进焉。具舟樯犯风涛。以求不死之人长生之药。乃于我国之西海。指点云水之间曰。蓬莱方丈在彼也。珠宫贝阙可到也。斋戒致诚。庶几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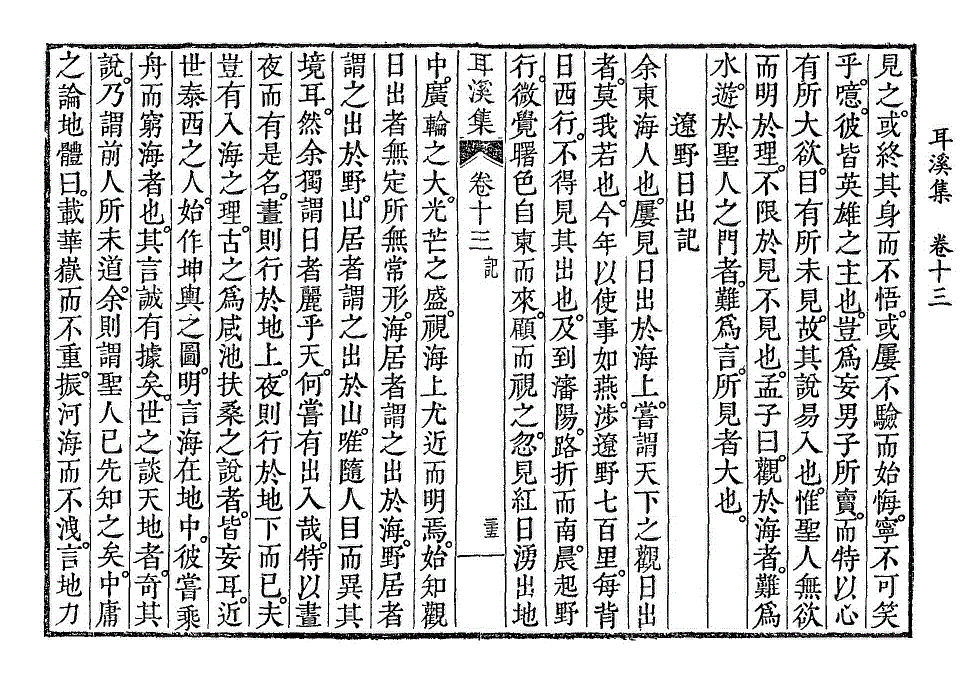 见之。或终其身而不悟。或屡不验而始悔。宁不可笑乎。噫。彼皆英雄之主也。岂为妄男子所卖。而特以心有所大欲。目有所未见。故其说易入也。惟圣人无欲而明于理。不限于见不见也。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所见者大也。
见之。或终其身而不悟。或屡不验而始悔。宁不可笑乎。噫。彼皆英雄之主也。岂为妄男子所卖。而特以心有所大欲。目有所未见。故其说易入也。惟圣人无欲而明于理。不限于见不见也。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所见者大也。辽野日出记
余东海人也。屡见日出于海上。尝谓天下之观日出者。莫我若也。今年以使事如燕。涉辽野七百里。每背日西行。不得见其出也。及到沈阳。路折而南。晨起野行。微觉曙色自东而来。顾而视之。忽见红日涌出地中。广轮之大。光芒之盛。视海上尤近而明焉。始知观日出者无定所无常形。海居者谓之出于海。野居者谓之出于野。山居者谓之出于山。唯随人目而异其境耳。然余独谓日者丽乎天。何尝有出入哉。特以昼夜而有是名。昼则行于地上。夜则行于地下而已。夫岂有入海之理。古之为咸池扶桑之说者。皆妄耳。近世泰西之人。始作坤舆之图。明言海在地中。彼尝乘舟而穷海者也。其言诚有据矣。世之谈天地者。奇其说。乃谓前人所未道。余则谓圣人已先知之矣。中庸之论地体曰。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言地力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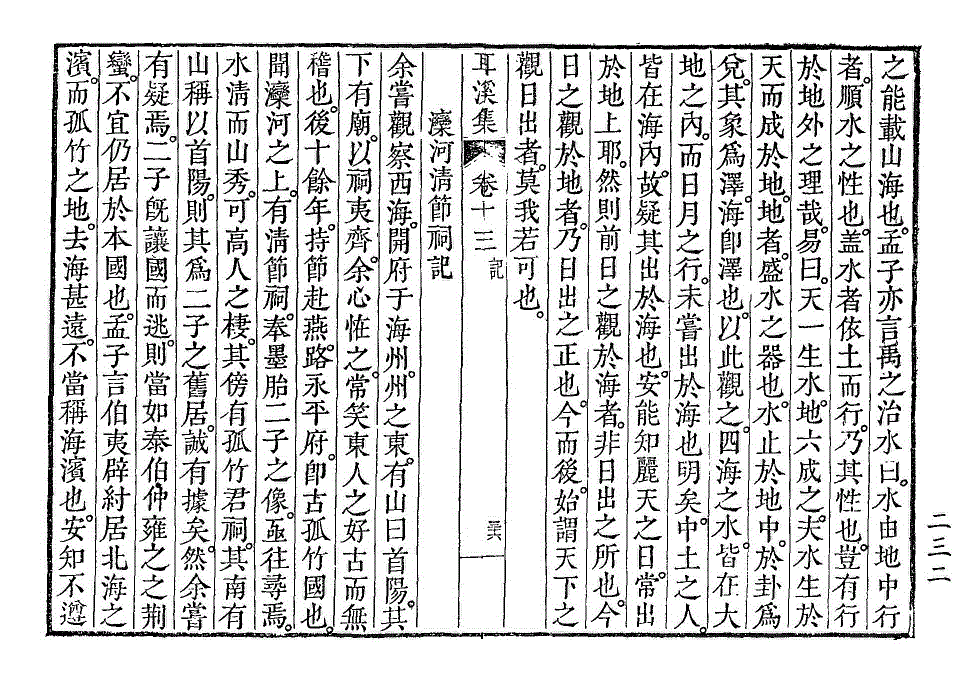 之能载山海也。孟子亦言禹之治水曰。水由地中行者。顺水之性也。盖水者依土而行。乃其性也。岂有行于地外之理哉。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水生于天而成于地。地者。盛水之器也。水止于地中。于卦为兑。其象为泽。海即泽也。以此观之。四海之水。皆在大地之内。而日月之行。未尝出于海也明矣。中土之人。皆在海内。故疑其出于海也。安能知丽天之日。常出于地上耶。然则前日之观于海者。非日出之所也。今日之观于地者。乃日出之正也。今而后。始谓天下之观日出者。莫我若可也。
之能载山海也。孟子亦言禹之治水曰。水由地中行者。顺水之性也。盖水者依土而行。乃其性也。岂有行于地外之理哉。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水生于天而成于地。地者。盛水之器也。水止于地中。于卦为兑。其象为泽。海即泽也。以此观之。四海之水。皆在大地之内。而日月之行。未尝出于海也明矣。中土之人。皆在海内。故疑其出于海也。安能知丽天之日。常出于地上耶。然则前日之观于海者。非日出之所也。今日之观于地者。乃日出之正也。今而后。始谓天下之观日出者。莫我若可也。滦河清节祠记
余尝观察西海。开府于海州。州之东。有山曰首阳。其下有庙。以祠夷齐。余心怪之。常笑东人之好古而无稽也。后十馀年。持节赴燕。路永平府。即古孤竹国也。闻滦河之上。有清节祠。奉墨胎二子之像。亟往寻焉。水清而山秀。可高人之栖。其傍有孤竹君祠。其南有山称以首阳。则其为二子之旧居。诚有据矣。然余尝有疑焉。二子既让国而逃。则当如泰伯,仲雍之之荆蛮。不宜仍居于本国也。孟子言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而孤竹之地。去海甚远。不当称海滨也。安知不遵
耳溪集卷十三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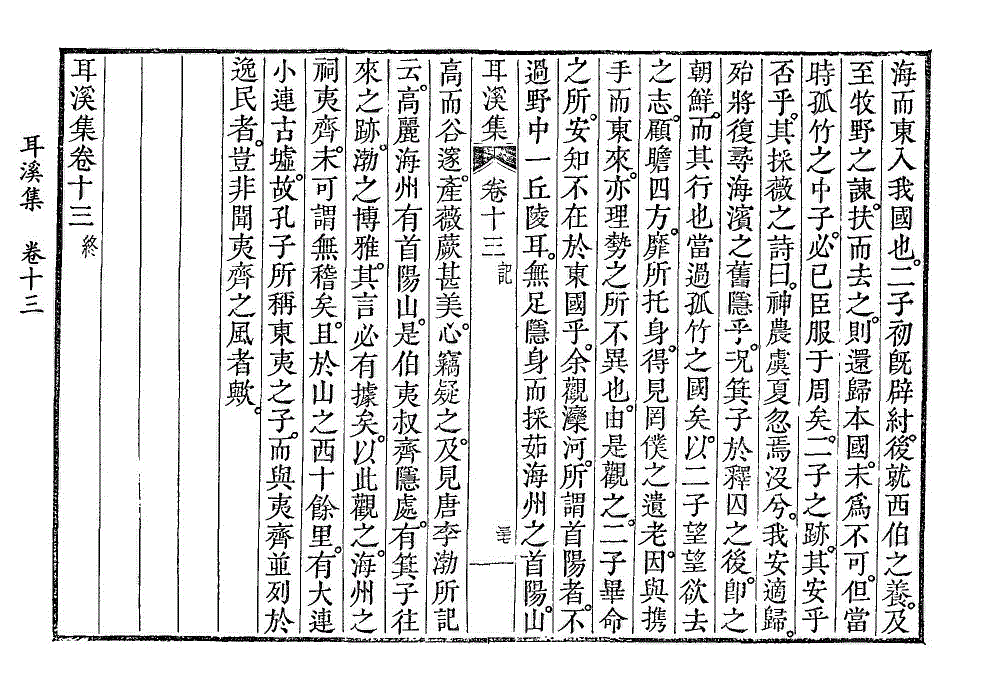 海而东入我国也。二子初既辟纣。后就西伯之养。及至牧野之谏。扶而去之。则还归本国。未为不可。但当时孤竹之中子。必已臣服于周矣。二子之迹。其安乎否乎。其采薇之诗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殆将复寻海滨之旧隐乎。况箕子于释囚之后。即之朝鲜。而其行也当过孤竹之国矣。以二子望望欲去之志。顾瞻四方。靡所托身。得见罔仆之遗老。因与携手而东来。亦理势之所不异也。由是观之。二子毕命之所。安知不在于东国乎。余观滦河。所谓首阳者。不过野中一丘陵耳。无足隐身而采茹。海州之首阳。山高而谷邃。产薇蕨甚美。心窃疑之。及见唐李渤所记云。高丽海州有首阳山。是伯夷,叔齐隐处。有箕子往来之迹。渤之博雅。其言必有据矣。以此观之。海州之祠夷,齐。未可谓无稽矣。且于山之西十馀里。有大连小连古墟。故孔子所称东夷之子。而与夷,齐并列于逸民者。岂非闻夷,齐之风者欤。
海而东入我国也。二子初既辟纣。后就西伯之养。及至牧野之谏。扶而去之。则还归本国。未为不可。但当时孤竹之中子。必已臣服于周矣。二子之迹。其安乎否乎。其采薇之诗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殆将复寻海滨之旧隐乎。况箕子于释囚之后。即之朝鲜。而其行也当过孤竹之国矣。以二子望望欲去之志。顾瞻四方。靡所托身。得见罔仆之遗老。因与携手而东来。亦理势之所不异也。由是观之。二子毕命之所。安知不在于东国乎。余观滦河。所谓首阳者。不过野中一丘陵耳。无足隐身而采茹。海州之首阳。山高而谷邃。产薇蕨甚美。心窃疑之。及见唐李渤所记云。高丽海州有首阳山。是伯夷,叔齐隐处。有箕子往来之迹。渤之博雅。其言必有据矣。以此观之。海州之祠夷,齐。未可谓无稽矣。且于山之西十馀里。有大连小连古墟。故孔子所称东夷之子。而与夷,齐并列于逸民者。岂非闻夷,齐之风者欤。耳溪集卷十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