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x 页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
序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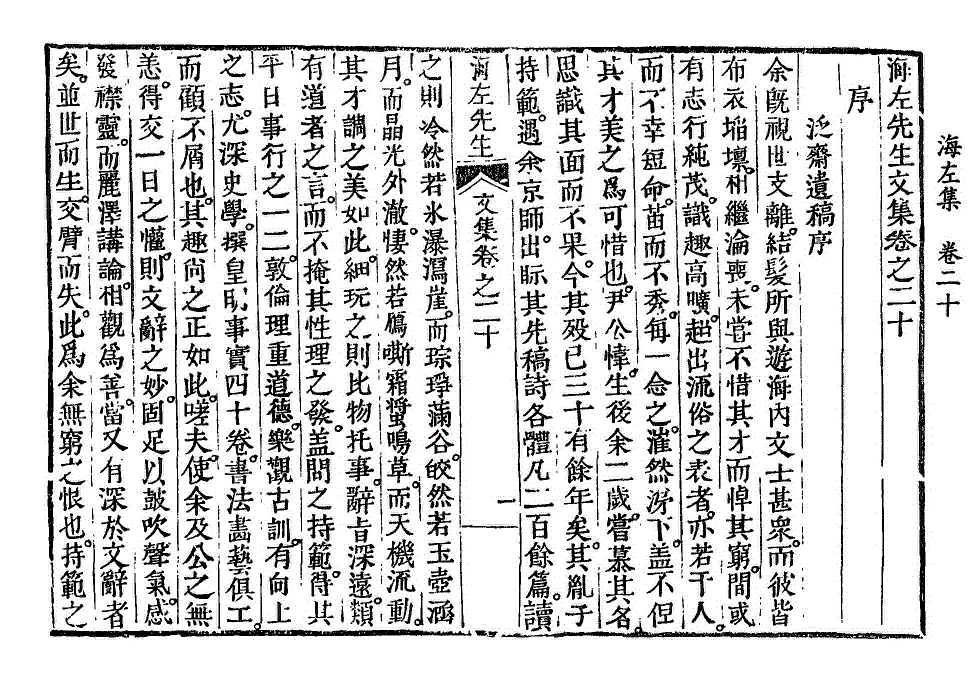 泛斋遗稿序
泛斋遗稿序余既视世支离。结发所与游海内文士甚众。而彼皆布衣埳壈。相继沦丧。未尝不惜其才而悼其穷。间或有志行纯茂。识趣高旷。超出流俗之表者。亦若干人。而不幸短命。苗而不秀。每一念之。漼然涕下。盖不但其才美之为可惜也。尹公愇。生后余二岁。尝慕其名。思识其面而不果。今其殁已三十有馀年矣。其胤子持范。遇余京师。出视其先稿诗各体凡二百馀篇。读之则冷然若冰瀑泻崖。而琮琤满谷。皎然若玉壶涵月。而晶光外澈。悽然若雁嘶霜螀鸣草。而天机流动。其才调之美如此。细玩之则比物托事。辞旨深远。类有道者之言。而不掩其性理之发。盖问之持范。得其平日事行之一二。敦伦理重道德。乐观古训。有向上之志。尤深史学。撰皇明事实四十卷。书法画艺俱工。而顾不屑也。其趣尚之正如此。嗟夫。使余及公之无恙。得交一日之欢。则文辞之妙。固足以鼓吹声气。感发襟灵。而丽泽讲论。相观为善。当又有深于文辞者矣。并世而生。交臂而失。此为余无穷之恨也。持范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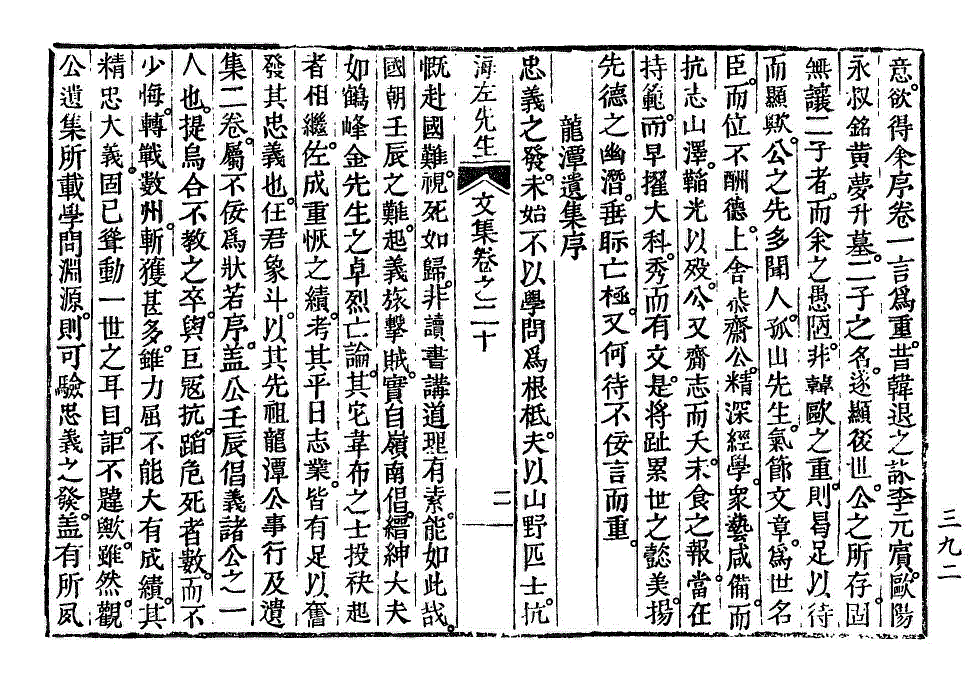 意。欲得余序卷一言为重。昔韩退之咏李元宾。欧阳永叔铭黄梦升墓。二子之名。遂显后世。公之所存。固无让二子者。而余之愚陋。非韩欧之重。则曷足以待而显欤。公之先多闻人。孤山先生。气节文章。为世名臣。而位不酬德。上舍恭斋公。精深经学。众艺咸备。而抗志山泽。韬光以殁。公又赍志而夭。未食之报。当在持范。而早擢大科。秀而有文。是将趾累世之懿美。扬先德之幽潜。垂视亡极。又何待不佞言而重。
意。欲得余序卷一言为重。昔韩退之咏李元宾。欧阳永叔铭黄梦升墓。二子之名。遂显后世。公之所存。固无让二子者。而余之愚陋。非韩欧之重。则曷足以待而显欤。公之先多闻人。孤山先生。气节文章。为世名臣。而位不酬德。上舍恭斋公。精深经学。众艺咸备。而抗志山泽。韬光以殁。公又赍志而夭。未食之报。当在持范。而早擢大科。秀而有文。是将趾累世之懿美。扬先德之幽潜。垂视亡极。又何待不佞言而重。龙潭遗集序
忠义之发。未始不以学问为根柢。夫以山野匹士。抗慨赴国难。视死如归。非读书讲道理有素。能如此哉。国朝壬辰之难。起义旅击贼。实自岭南倡。缙绅大夫如鹤峰金先生之卓烈亡论。其它韦布之士投袂起者相继。佐成重恢之绩。考其平日志业。皆有足以奋发其忠义也。任君象斗。以其先祖龙潭公事行及遗集二卷。属不佞为状若序。盖公壬辰倡义诸公之一人也。提乌合不教之卒。与巨寇抗。蹈危死者数。而不少悔。转战数州。斩获甚多。虽力屈不能大有成绩。其精忠大义。固已耸动一世之耳目。讵不韪欤。虽然。观公遗集所载学问渊源。则可验忠义之发。盖有所夙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3H 页
 讲也。公尝师事朴啸皋,郑寒岗二先生。又与同时诸儒贤。商质问难。治心之要。则于裒集古训恒诵篇。可知。议礼之详。则于冠婚丧祭往复诸书。可知。其践履思辨之实如此。性情之感而为诗文诸作。又古质冲雅。不掩其有德之言。积之躬而为学问。施之事而为忠义。体用源流之相须。有不可诬者也。昔杜子美当天宝之乱。伤君父之蒙尘。痛逆胡之猾夏。孤诚幽愤。形诸赋咏之间。论者谓子美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读北征诸诗。可验其所存。后之君子读公集而不知公之所存。其可乎哉。遂述其语。为龙潭集序。
讲也。公尝师事朴啸皋,郑寒岗二先生。又与同时诸儒贤。商质问难。治心之要。则于裒集古训恒诵篇。可知。议礼之详。则于冠婚丧祭往复诸书。可知。其践履思辨之实如此。性情之感而为诗文诸作。又古质冲雅。不掩其有德之言。积之躬而为学问。施之事而为忠义。体用源流之相须。有不可诬者也。昔杜子美当天宝之乱。伤君父之蒙尘。痛逆胡之猾夏。孤诚幽愤。形诸赋咏之间。论者谓子美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读北征诸诗。可验其所存。后之君子读公集而不知公之所存。其可乎哉。遂述其语。为龙潭集序。兀山遗稿序
中和之在人性。天所赋也。得之天者全。则外物之感。莫得以铄之。故发之声音而为文章议论者。有夷旷之识。而无感愤怨尤之意。彼三百篇作者。随运世污隆。而正变尔殊者。是其人未必皆贤者也。余于近时东表。得一人焉。兀山赵公是已。嗟夫。公之所遇。可谓穷矣。门户之显。则世禄仕家衣冠。而沦而为布褐。朋游之盛。则轩轾名胜。唱酬相乐。而去而为钓徒樵伴。据上游而为园林楼榭者。不知几易主。而穹林绝巘井落之间。鹿豕之迹交错。此常情之所不能堪。而自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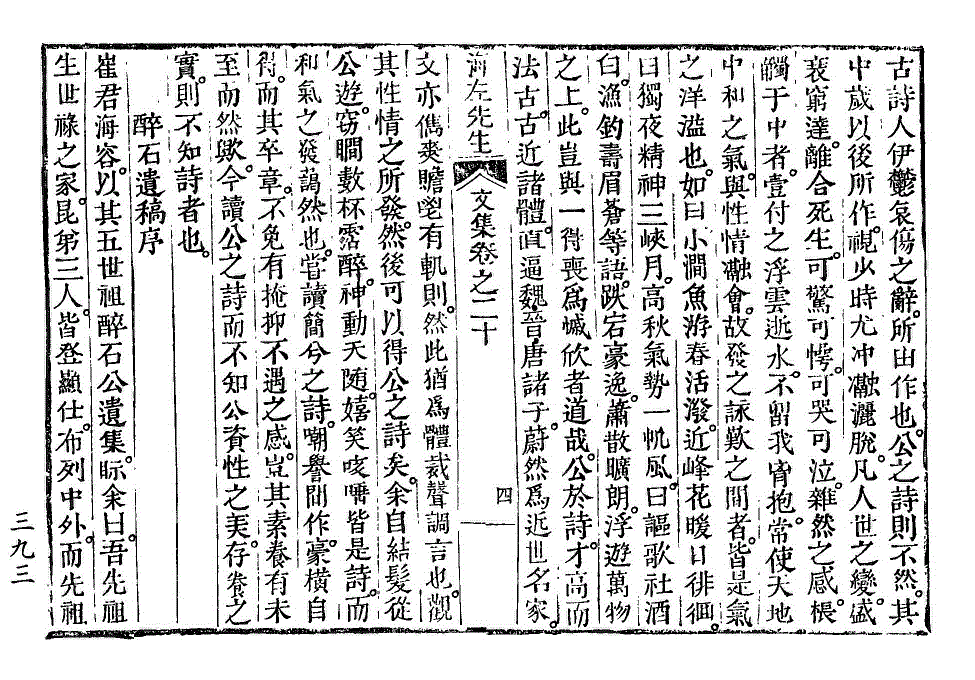 古诗人伊郁哀伤之辞。所由作也。公之诗则不然。其中岁以后所作。视少时尤冲瀜洒脱。凡人世之变。盛衰穷达。离合死生。可惊可愕。可哭可泣。杂然之感。枨触于中者。壹付之浮云逝水。不留我胸抱。常使天地中和之气。与性情瀜会。故发之咏叹之间者。皆是气之洋溢也。如曰小涧鱼游春活泼。近峰花暖日徘徊。曰独夜精神三峡月。高秋气势一帆风。曰讴歌社酒白。渔钓寿眉苍等语。跌宕豪逸。萧散旷朗。浮游万物之上。此岂与一得丧为戚欣者道哉。公于诗。才高而法古。古近诸体。直逼魏,晋,唐诸子。蔚然为近世名家。文亦俊爽赡鬯有䡄则。然此犹为体裁声调言也。观其性情之所发。然后可以得公之诗矣。余自结发从公游。窃瞷数杯沾醉。神动天随。嬉笑咳唾皆是诗。而和气之发蔼然也。尝读简兮之诗。嘲誉问作。豪横自得。而其卒章。不免有掩抑不遇之感。岂其素养有未至而然欤。今读公之诗而不知公资性之美。存养之实。则不知诗者也。
古诗人伊郁哀伤之辞。所由作也。公之诗则不然。其中岁以后所作。视少时尤冲瀜洒脱。凡人世之变。盛衰穷达。离合死生。可惊可愕。可哭可泣。杂然之感。枨触于中者。壹付之浮云逝水。不留我胸抱。常使天地中和之气。与性情瀜会。故发之咏叹之间者。皆是气之洋溢也。如曰小涧鱼游春活泼。近峰花暖日徘徊。曰独夜精神三峡月。高秋气势一帆风。曰讴歌社酒白。渔钓寿眉苍等语。跌宕豪逸。萧散旷朗。浮游万物之上。此岂与一得丧为戚欣者道哉。公于诗。才高而法古。古近诸体。直逼魏,晋,唐诸子。蔚然为近世名家。文亦俊爽赡鬯有䡄则。然此犹为体裁声调言也。观其性情之所发。然后可以得公之诗矣。余自结发从公游。窃瞷数杯沾醉。神动天随。嬉笑咳唾皆是诗。而和气之发蔼然也。尝读简兮之诗。嘲誉问作。豪横自得。而其卒章。不免有掩抑不遇之感。岂其素养有未至而然欤。今读公之诗而不知公资性之美。存养之实。则不知诗者也。醉石遗稿序
崔君海容。以其五世祖醉石公遗集。视余曰。吾先祖生世禄之家。昆弟三人。皆登显仕。布列中外。而先祖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4H 页
 卓荦负高世气。不肯随俗进取。恣肆山水以没齿。博学喜文词。尤专于诗。所著述甚富。而不幸灾于火。先祖既穷而在下。才美不表见。空言垂后之业。残缺如此。百世孰知有吾先祖哉。幸执事惠一言为重。余应之曰。不然。通塞不系贤不肖久矣。自古乘贵势翔天逵者何限。而其中未必有衣布褐蓬蔂行。而往往怀抱利器尚论者。自当辨之矣。醉石公。当一家贵显时。趯然有遐举物表之意。与木石俱晦。非贤于人而能之乎。文章。要可传。不在篇什之多寡。千羊之皮。其将与一狐白同价哉。公之诗天才甚高。辅以古学。上规三唐。下不失宋人风旨。而一种清虚澹一之气。类不食烟火人语。文亦信笔滔滔。无褊迫涩僻之态。虽其全藁灰烬。为可恨。零金碎玉。犹是希世宝子。姑十袭以俟。是必有光怪之发。辉映关东草木。而为望气者所赏识尔。
卓荦负高世气。不肯随俗进取。恣肆山水以没齿。博学喜文词。尤专于诗。所著述甚富。而不幸灾于火。先祖既穷而在下。才美不表见。空言垂后之业。残缺如此。百世孰知有吾先祖哉。幸执事惠一言为重。余应之曰。不然。通塞不系贤不肖久矣。自古乘贵势翔天逵者何限。而其中未必有衣布褐蓬蔂行。而往往怀抱利器尚论者。自当辨之矣。醉石公。当一家贵显时。趯然有遐举物表之意。与木石俱晦。非贤于人而能之乎。文章。要可传。不在篇什之多寡。千羊之皮。其将与一狐白同价哉。公之诗天才甚高。辅以古学。上规三唐。下不失宋人风旨。而一种清虚澹一之气。类不食烟火人语。文亦信笔滔滔。无褊迫涩僻之态。虽其全藁灰烬。为可恨。零金碎玉。犹是希世宝子。姑十袭以俟。是必有光怪之发。辉映关东草木。而为望气者所赏识尔。石门遗稿序
诗亡它道。原本性情。发宣其所欲言而已。故有以雕琢章句。鼓吹声律为工者。有以典赡醇质。词理俱鬯为工者。虽体裁不同。而其为诗则一也。余少时闻石门柳公博学好古。工书法。顾数畸。布衣以歾。为士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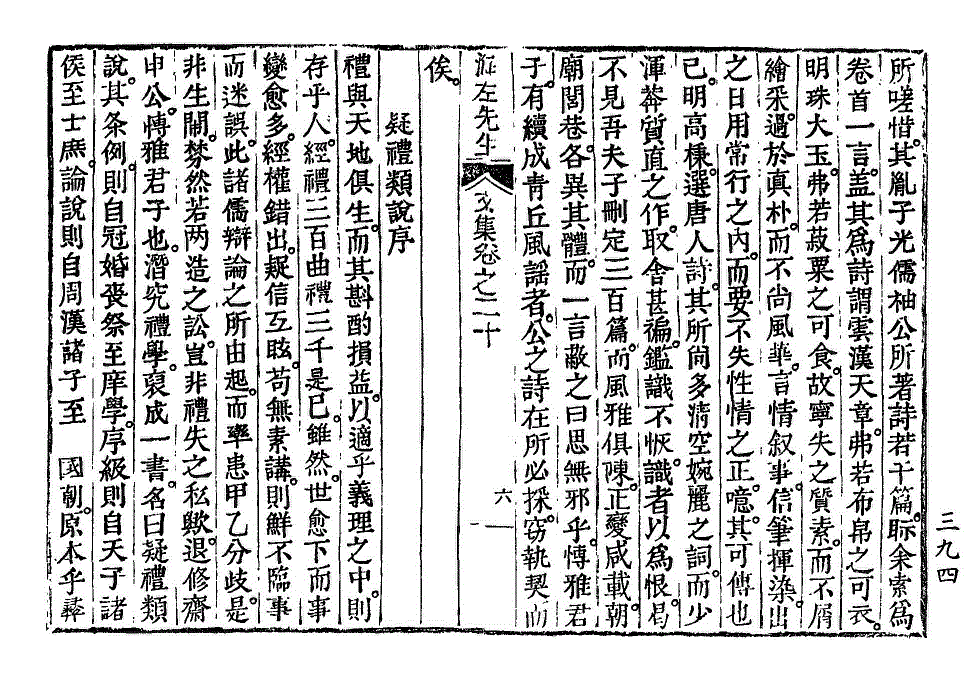 所嗟惜。其胤子光儒袖公所著诗若干篇。视余索为卷首一言。盖其为诗谓云汉天章。弗若布帛之可衣。明珠大玉。弗若菽粟之可食。故宁失之质素。而不屑绘采。过于真朴。而不尚风华。言情叙事。信笔挥染。出之日用常行之内。而要不失性情之正。噫。其可传也已。明高柄。选唐人诗。其所尚多清空婉丽之词。而少浑莽质直之作。取舍甚褊。鉴识不恢。识者以为恨。曷不见吾夫子删定三百篇。而风雅俱陈。正变咸载。朝庙闾巷。各异其体。而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乎。博雅君子。有续成青丘风谣者。公之诗在所必采。窃执契而俟。
所嗟惜。其胤子光儒袖公所著诗若干篇。视余索为卷首一言。盖其为诗谓云汉天章。弗若布帛之可衣。明珠大玉。弗若菽粟之可食。故宁失之质素。而不屑绘采。过于真朴。而不尚风华。言情叙事。信笔挥染。出之日用常行之内。而要不失性情之正。噫。其可传也已。明高柄。选唐人诗。其所尚多清空婉丽之词。而少浑莽质直之作。取舍甚褊。鉴识不恢。识者以为恨。曷不见吾夫子删定三百篇。而风雅俱陈。正变咸载。朝庙闾巷。各异其体。而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乎。博雅君子。有续成青丘风谣者。公之诗在所必采。窃执契而俟。疑礼类说序
礼与天地俱生。而其斟酌损益。以适乎义理之中。则存乎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已。虽然。世愈下而事变愈多。经权错出。疑信互眩。苟无素讲。则鲜不临事而迷误。此诸儒辩论之所由起。而率患甲乙分歧。是非生闹。棼然若两造之讼。岂非礼失之私欤。退修斋申公。博雅君子也。潜究礼学。裒成一书。名曰疑礼类说。其条例。则自冠婚丧祭至庠学。序级则自天子诸侯至士庶。论说则自周汉诸子至 国朝。原本乎彝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5H 页
 伦日用。会通乎天理人情。开卷读之。有可以直据而仿行者。有可以参考而折衷者。有可以旁照而义起者。虽当仓卒非常之境。而自无眩乱失措之患。譬如阅一幅舆地图。山川之险夷。道里之回直。风壤之薄厚。举目洞然。在行者审择向背。惟意所适。奚待指南车而导迷哉。且其全书。裒杂众说。长短俱载。而未尝自立意见。勘断彼此。使学者。讲究而自得之。其识度虚旷。了无物我之私。而卓越诸家可知已。使是书行于世。则其所以嘉惠学士。裨益世道。岂其微哉。公之胤子夭殁。嗣孙稚幼。巾衍之藏。历三十馀年。而墨迹䵝昧。幸而公之馀子达渊。惟堙晦是惧。竭诚经纪。将锓之梓。属不佞为简首一言。不辞而为之序。
伦日用。会通乎天理人情。开卷读之。有可以直据而仿行者。有可以参考而折衷者。有可以旁照而义起者。虽当仓卒非常之境。而自无眩乱失措之患。譬如阅一幅舆地图。山川之险夷。道里之回直。风壤之薄厚。举目洞然。在行者审择向背。惟意所适。奚待指南车而导迷哉。且其全书。裒杂众说。长短俱载。而未尝自立意见。勘断彼此。使学者。讲究而自得之。其识度虚旷。了无物我之私。而卓越诸家可知已。使是书行于世。则其所以嘉惠学士。裨益世道。岂其微哉。公之胤子夭殁。嗣孙稚幼。巾衍之藏。历三十馀年。而墨迹䵝昧。幸而公之馀子达渊。惟堙晦是惧。竭诚经纪。将锓之梓。属不佞为简首一言。不辞而为之序。下枝集序
下枝李公。孤山先生之闻孙也。先生邃学懿行。为山南师表。与不佞高王考愚潭先生。道义相契。讲论往复甚乐。而不佞尝猥撰先生墓志及遗集序。盖与公世好笃挚。而顾居远不得一识面。为平生恨。公殁之二十二年。公之弟弘辰氏。以公所著诗文寄视。属不佞为卷首一言。乌敢辞。山南被儒贤教化。学士大夫重道德崇经术。故其文章深博如渊海。议论可以补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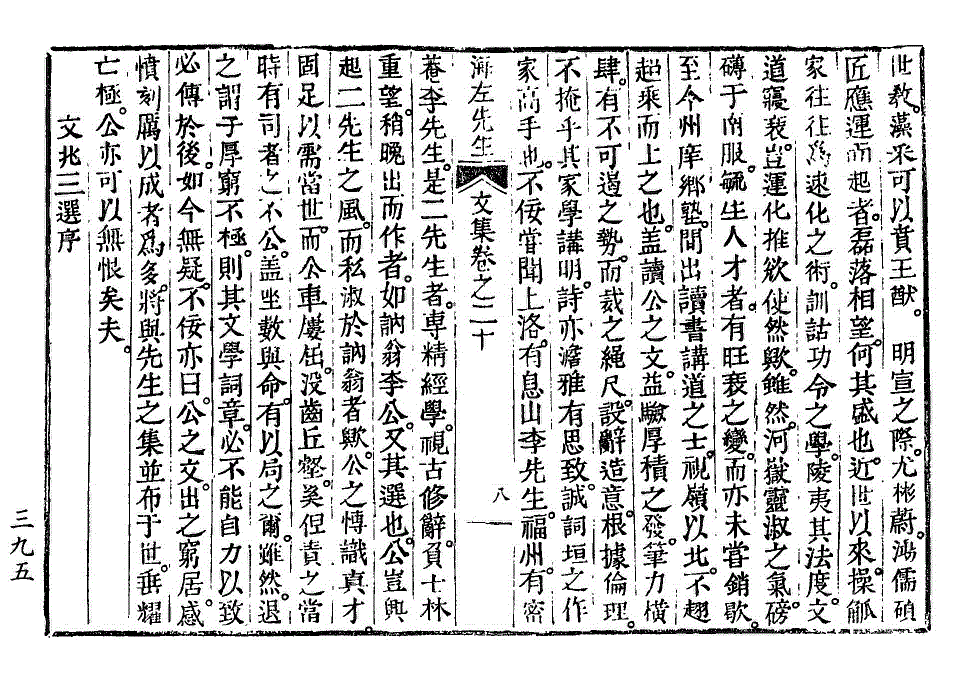 世教。藻采可以贲王猷。 明宣之际。尤彬蔚。鸿儒硕匠应运而起者。磊落相望。何其盛也。近世以来。操觚家往往为速化之术。训诂功令之学。陵夷其法度。文道寝衰。岂运化推敚使然欤。虽然。河岳灵淑之气。磅礴于南服。毓生人才者。有旺衰之变。而亦未尝销歇。至今州庠乡塾。间出读书讲道之士。视岭以北。不趐超乘而上之也。盖读公之文。益验厚积之发。笔力横肆。有不可遏之势。而裁之绳尺。设辞造意。根据伦理。不掩乎其家学讲明。诗亦澹雅有思致。诚词垣之作家高手也。不佞尝闻上洛。有息山李先生。福州。有密庵李先生。是二先生者。专精经学。视古修辞。负士林重望。稍晚出而作者。如讷翁李公。又其选也。公岂兴起二先生之风。而私淑于讷翁者欤。公之博识真才。固足以需当世。而公车屡屈。没齿丘壑。奚但责之当时有司者之不公。盖坐数与命。有以局之尔。虽然。退之谓子厚穷不极。则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不佞亦曰公之文。出之穷居。感愤刻厉以成者为多。将与先生之集并布于世。垂耀亡极。公亦可以无恨矣夫。
世教。藻采可以贲王猷。 明宣之际。尤彬蔚。鸿儒硕匠应运而起者。磊落相望。何其盛也。近世以来。操觚家往往为速化之术。训诂功令之学。陵夷其法度。文道寝衰。岂运化推敚使然欤。虽然。河岳灵淑之气。磅礴于南服。毓生人才者。有旺衰之变。而亦未尝销歇。至今州庠乡塾。间出读书讲道之士。视岭以北。不趐超乘而上之也。盖读公之文。益验厚积之发。笔力横肆。有不可遏之势。而裁之绳尺。设辞造意。根据伦理。不掩乎其家学讲明。诗亦澹雅有思致。诚词垣之作家高手也。不佞尝闻上洛。有息山李先生。福州。有密庵李先生。是二先生者。专精经学。视古修辞。负士林重望。稍晚出而作者。如讷翁李公。又其选也。公岂兴起二先生之风。而私淑于讷翁者欤。公之博识真才。固足以需当世。而公车屡屈。没齿丘壑。奚但责之当时有司者之不公。盖坐数与命。有以局之尔。虽然。退之谓子厚穷不极。则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不佞亦曰公之文。出之穷居。感愤刻厉以成者为多。将与先生之集并布于世。垂耀亡极。公亦可以无恨矣夫。文兆三选序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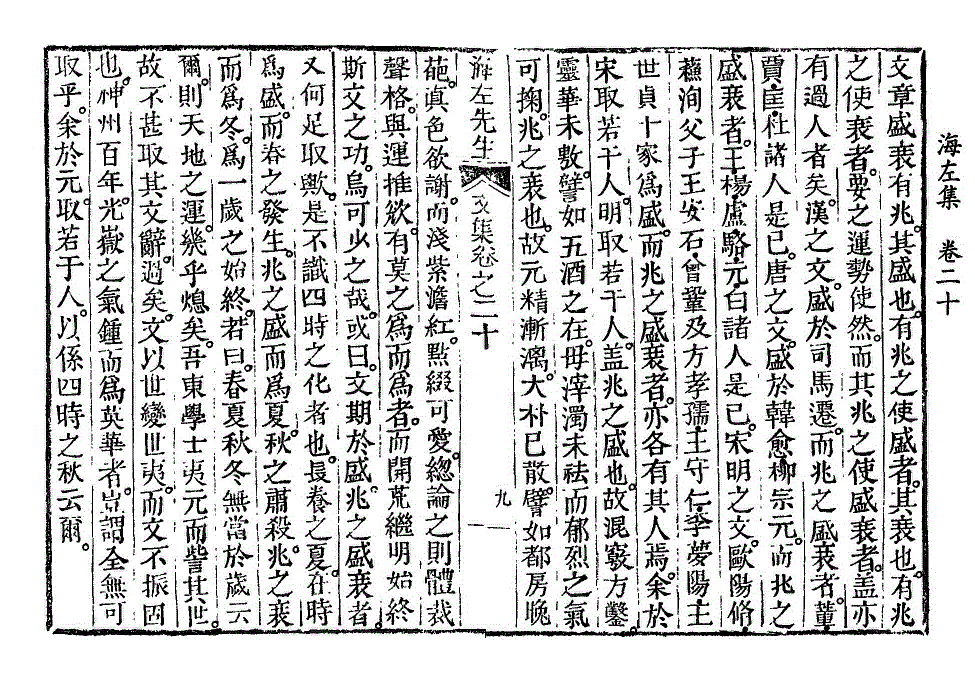 文章盛衰有兆。其盛也。有兆之使盛者。其衰也。有兆之使衰者。要之运势使然。而其兆之使盛衰者。盖亦有过人者矣。汉之文。盛于司马迁。而兆之盛衰者。蕫,贾,匡,杜诸人是已。唐之文。盛于韩愈,柳宗元。而兆之盛衰者王,杨,卢,骆,元,白诸人是已。宋明之文。欧阳脩,苏洵父子王安石,曾巩及方孝孺,王守仁,李梦阳,王世贞十家为盛。而兆之盛衰者。亦各有其人焉。余于宋取若干人。明取若干人。盖兆之盛也。故混窍方凿。灵华未敷。譬如五酒之在。毋滓浊未祛而郁烈之气可掬。兆之衰也。故元精渐漓。大朴已散。譬如都房晚葩。真色欲谢。而浅紫澹红。点缀可爱。总论之则体裁声格。与运推敚。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开荒继明始终斯文之功。乌可少之哉。或曰。文期于盛。兆之盛衰者。又何足取欤。是不识四时之化者也。长养之夏。在时为盛。而春之发生。兆之盛而为夏。秋之肃杀。兆之衰而为冬。为一岁之始终。若曰。春夏秋冬无当于岁云尔。则天地之运。几乎熄矣。吾东学士夷元而訾其世。故不甚取其文辞。过矣。文以世变世夷。而文不振固也。神州百年。光岳之气钟而为英华者。岂谓全无可取乎。余于元。取若干人。以系四时之秋云尔。
文章盛衰有兆。其盛也。有兆之使盛者。其衰也。有兆之使衰者。要之运势使然。而其兆之使盛衰者。盖亦有过人者矣。汉之文。盛于司马迁。而兆之盛衰者。蕫,贾,匡,杜诸人是已。唐之文。盛于韩愈,柳宗元。而兆之盛衰者王,杨,卢,骆,元,白诸人是已。宋明之文。欧阳脩,苏洵父子王安石,曾巩及方孝孺,王守仁,李梦阳,王世贞十家为盛。而兆之盛衰者。亦各有其人焉。余于宋取若干人。明取若干人。盖兆之盛也。故混窍方凿。灵华未敷。譬如五酒之在。毋滓浊未祛而郁烈之气可掬。兆之衰也。故元精渐漓。大朴已散。譬如都房晚葩。真色欲谢。而浅紫澹红。点缀可爱。总论之则体裁声格。与运推敚。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开荒继明始终斯文之功。乌可少之哉。或曰。文期于盛。兆之盛衰者。又何足取欤。是不识四时之化者也。长养之夏。在时为盛。而春之发生。兆之盛而为夏。秋之肃杀。兆之衰而为冬。为一岁之始终。若曰。春夏秋冬无当于岁云尔。则天地之运。几乎熄矣。吾东学士夷元而訾其世。故不甚取其文辞。过矣。文以世变世夷。而文不振固也。神州百年。光岳之气钟而为英华者。岂谓全无可取乎。余于元。取若干人。以系四时之秋云尔。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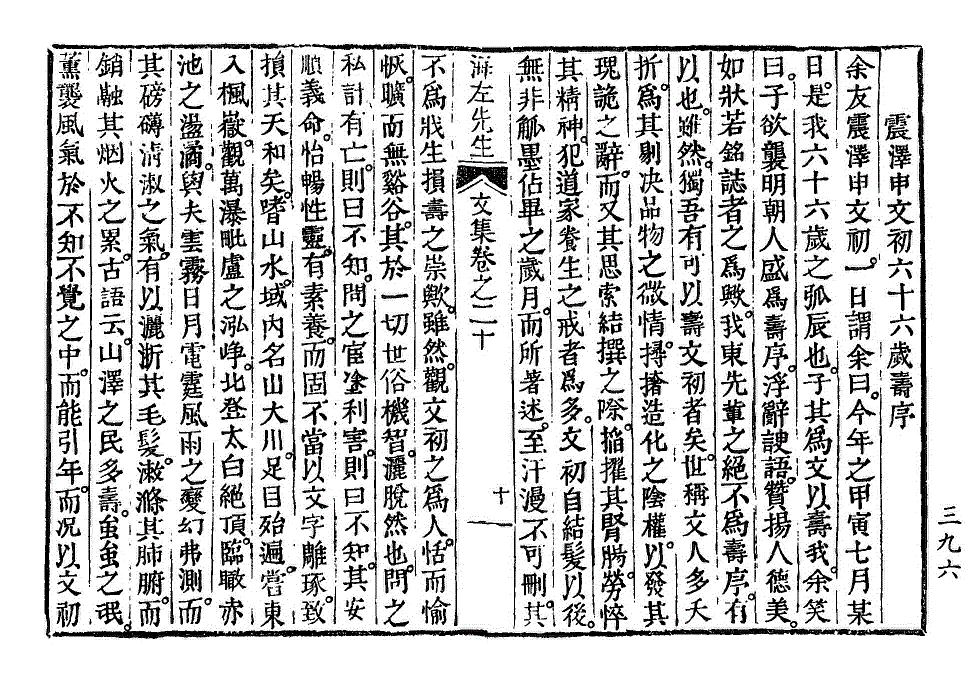 震泽申文初六十六岁寿序
震泽申文初六十六岁寿序余友震泽申文初。一日谓余曰。今年之甲寅七月某日。是我六十六岁之弧辰也。子其为文以寿我。余笑曰。子欲袭明朝人盛为寿序。浮辞谀语。赞扬人德美。如状若铭志者之为欤。我东先辈之绝不为寿序。有以也。虽然。独吾有可以寿文初者矣。世称文人多夭折。为其剔决品物之微情。挦扯造化之阴权。以发其瑰诡之辞。而又其思索结撰之际。搯擢其肾肠。劳悴其精神。犯道家养生之戒者为多。文初自结发以后。无非觚墨佔毕之岁月。而所著述。至汗漫不可删。其不为戕生损寿之祟欤。虽然。观文初之为人。恬而愉恢。旷而无溪谷。其于一切世俗机智。洒脱然也。问之私计有亡。则曰不知。问之宦涂利害。则曰不知。其安顺义命。怡畅性灵。有素养。而固不当以文字雕琢。致损其天和矣。嗜山水。域内名山大川。足目殆遍。尝东入枫岳。观万瀑,毗卢之泓峥。北登太白绝顶。临瞰赤池之荡潏。与夫云雾日月电霆风雨之变幻弗测。而其磅礴清淑之气。有以洒浙其毛发。漱涤其肺腑。而销融其烟火之累。古语云。山泽之民多寿。蚩蚩之氓。薰袭风气于不知不觉之中。而能引年。而况以文初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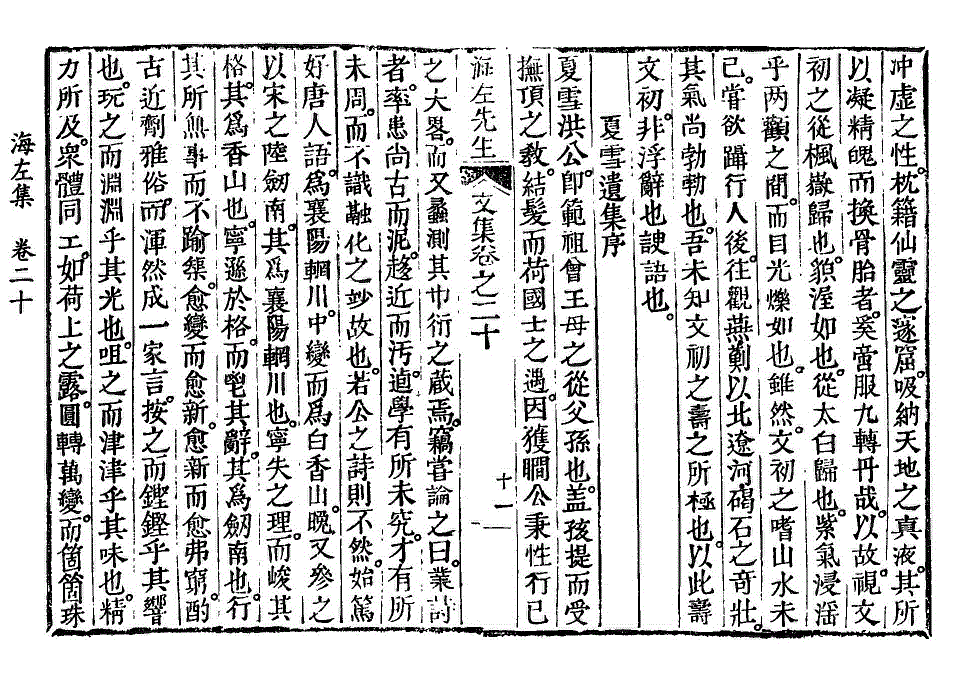 冲虚之性。枕籍仙灵之邃窟。吸纳天地之真液。其所以凝精魄而换骨胎者。奚啻服九转丹哉。以故。视文初之从枫岳归也。貌渥如也。从太白归也。紫气浸淫乎两颧之间。而目光烁如也。虽然。文初之嗜山水未已。尝欲蹑行人后。往观燕,蓟以北辽河,碣石之奇壮。其气尚勃勃也。吾未知文初之寿之所极也。以此寿文初。非浮辞也谀语也。
冲虚之性。枕籍仙灵之邃窟。吸纳天地之真液。其所以凝精魄而换骨胎者。奚啻服九转丹哉。以故。视文初之从枫岳归也。貌渥如也。从太白归也。紫气浸淫乎两颧之间。而目光烁如也。虽然。文初之嗜山水未已。尝欲蹑行人后。往观燕,蓟以北辽河,碣石之奇壮。其气尚勃勃也。吾未知文初之寿之所极也。以此寿文初。非浮辞也谀语也。夏雪遗集序
夏雪洪公。即范祖曾王母之从父孙也。盖孩提而受抚顶之教。结发而荷国士之遇。因获瞷公秉性行己之大略。而又蠡测其巾衍之藏焉。窃尝论之曰。业诗者。率患尚古而泥。趍近而污。逌学有所未究。才有所未周。而不识融化之妙故也。若公之诗则不然。始笃好唐人语。为襄阳辋川。中变而为白香山。晚又参之以宋之陆剑南。其为襄阳辋川也。宁失之理。而峻其格。其为香山也。宁逊于格。而鬯其辞。其为剑南也。行其所无事而不踰矩。愈变而愈新。愈新而愈弗穷。酌古近剂雅俗。而浑然成一家言。按之而铿铿乎其响也。玩之而渊渊乎其光也。咀之而津津乎其味也。精力所及。众体同工。如荷上之露。圆转万变。而个个珠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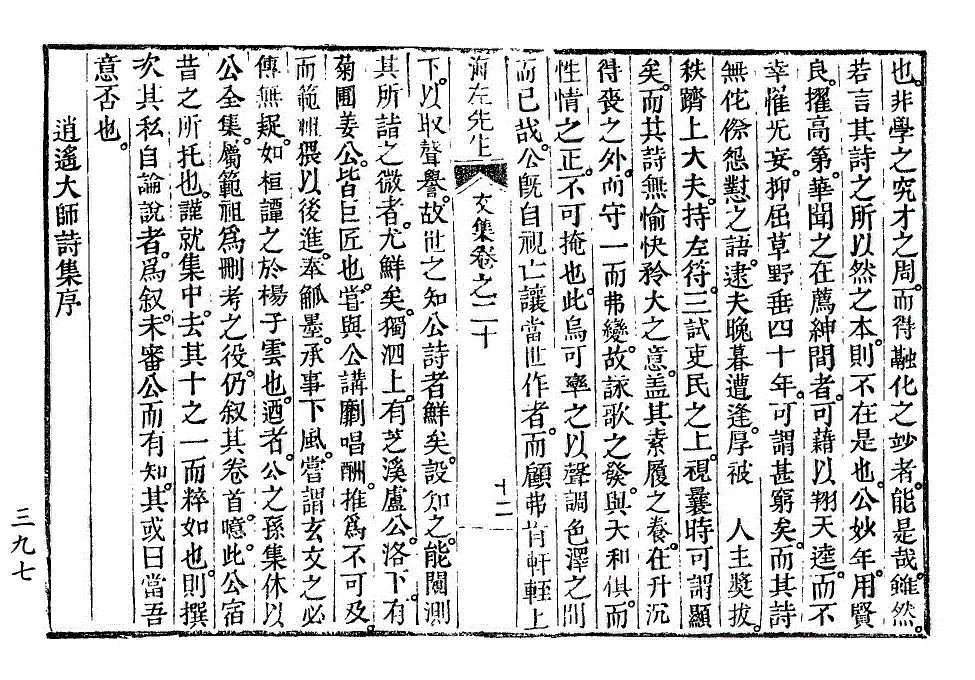 也。非学之究才之周。而得融化之妙者。能是哉。虽然。若言其诗之所以然之本。则不在是也。公妙年。用贤良。擢高第。华闻之在荐绅间者。可藉以翔天逵。而不幸罹无妄。抑屈草野垂四十年。可谓甚穷矣。而其诗无佗傺怨怼之语。逮夫晚暮遭逢。厚被 人主奖拔。秩跻上大夫。持左符。三试吏民之上。视曩时可谓显矣。而其诗无愉快矜大之意。盖其素履之养。在升沉得丧之外。而守一而弗变。故咏歌之发。与天和俱。而性情之正。不可掩也。此乌可率之以声调色泽之间而已哉。公既自视亡让当世作者。而顾弗肯轩轾上下。以取声誉。故世之知公诗者鲜矣。设知之。能窥测其所诣之微者。尤鲜矣。独泗上。有芝溪卢公。洛下。有菊圃姜公。皆巨匠也。尝与公讲劘唱酬。推为不可及。而范祖猥以后进。奉觚墨。承事下风。尝谓玄文之必传无疑。如桓谭之于杨子云也。乃者。公之孙集休以公全集。属范祖为删考之役。仍叙其卷首。噫。此公宿昔之所托也。谨就集中。去其十之一而粹如也。则撰次其私自论说者。为叙。未审公而有知。其或曰当吾意否也。
也。非学之究才之周。而得融化之妙者。能是哉。虽然。若言其诗之所以然之本。则不在是也。公妙年。用贤良。擢高第。华闻之在荐绅间者。可藉以翔天逵。而不幸罹无妄。抑屈草野垂四十年。可谓甚穷矣。而其诗无佗傺怨怼之语。逮夫晚暮遭逢。厚被 人主奖拔。秩跻上大夫。持左符。三试吏民之上。视曩时可谓显矣。而其诗无愉快矜大之意。盖其素履之养。在升沉得丧之外。而守一而弗变。故咏歌之发。与天和俱。而性情之正。不可掩也。此乌可率之以声调色泽之间而已哉。公既自视亡让当世作者。而顾弗肯轩轾上下。以取声誉。故世之知公诗者鲜矣。设知之。能窥测其所诣之微者。尤鲜矣。独泗上。有芝溪卢公。洛下。有菊圃姜公。皆巨匠也。尝与公讲劘唱酬。推为不可及。而范祖猥以后进。奉觚墨。承事下风。尝谓玄文之必传无疑。如桓谭之于杨子云也。乃者。公之孙集休以公全集。属范祖为删考之役。仍叙其卷首。噫。此公宿昔之所托也。谨就集中。去其十之一而粹如也。则撰次其私自论说者。为叙。未审公而有知。其或曰当吾意否也。逍遥大师诗集序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8H 页
 诗家以深于诗道。谓得禅悟。盖悟是佛氏之极功耳。虽然。诗造悟境甚难。世称王摩诘诗近禅悟。而其馀无闻焉。缁流之诗亦然。自六朝至三唐。号能诗者众。而未见其有悟解。岂彼其于禅学。有未甚悟故欤。一日顗上人。自潭阳之玉泉庵。飞锡八百里。谒余以其六世法祖逍遥大师诗集。属为叙。阅之。则诗止五七言律绝二百有四篇。而清空澹泊。如云过空。而月印川间。以名言妙喻。超诣色相之先。盖近于悟者也。问师法派。则曰是西山大师之嫡传弟子也。夫西山师。夙阐禅宗。妙契玄旨。慧观灵智。旁晓韬略。左右 王师。普济龙蛇之难。非洞悟万法一心。随类圆通之妙。能如是哉。法门衣钵。以悟传悟。无怪乎逍遥师之游戏三昧。悟及诗道也。师于茶毗之夕。双珠现瑞。塔而奉之。惟是二百四篇之诗。不趐双珠之宝重。则宜上人之乞言于余。欲垂之穷劫也。余尝为西山师。记其写照之阁。今于师之集。独靳于言乎。虽然。师既脱六尘超三界。视四大如蜩甲。咳唾之馀。曷足为师之有亡哉。上人曰。是固然矣。抑诗师之迹也。去吾师二百馀年之久。而求其髣髴。惟迹而已。因迹而慕。因慕而师斯存。乌可已乎。余感其意。而为之言如此。
诗家以深于诗道。谓得禅悟。盖悟是佛氏之极功耳。虽然。诗造悟境甚难。世称王摩诘诗近禅悟。而其馀无闻焉。缁流之诗亦然。自六朝至三唐。号能诗者众。而未见其有悟解。岂彼其于禅学。有未甚悟故欤。一日顗上人。自潭阳之玉泉庵。飞锡八百里。谒余以其六世法祖逍遥大师诗集。属为叙。阅之。则诗止五七言律绝二百有四篇。而清空澹泊。如云过空。而月印川间。以名言妙喻。超诣色相之先。盖近于悟者也。问师法派。则曰是西山大师之嫡传弟子也。夫西山师。夙阐禅宗。妙契玄旨。慧观灵智。旁晓韬略。左右 王师。普济龙蛇之难。非洞悟万法一心。随类圆通之妙。能如是哉。法门衣钵。以悟传悟。无怪乎逍遥师之游戏三昧。悟及诗道也。师于茶毗之夕。双珠现瑞。塔而奉之。惟是二百四篇之诗。不趐双珠之宝重。则宜上人之乞言于余。欲垂之穷劫也。余尝为西山师。记其写照之阁。今于师之集。独靳于言乎。虽然。师既脱六尘超三界。视四大如蜩甲。咳唾之馀。曷足为师之有亡哉。上人曰。是固然矣。抑诗师之迹也。去吾师二百馀年之久。而求其髣髴。惟迹而已。因迹而慕。因慕而师斯存。乌可已乎。余感其意。而为之言如此。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8L 页
 竹亭遗事序
竹亭遗事序士之传信后世。其道不一。或录其文辞。使后人。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或子孙门徒备述其德行言语。使后人。有所观感而兴起。均之为传世资也。虽然。文辞者。德行之发于外。而为绪馀者也。盖亦有本末轻重之辨焉尔。不佞读竹亭张公遗事。作而曰。是岂但外之为文辞而已哉。公天质明粹。乐读古训。尝从静庵赵先生。闻为学大方。又与晦斋,退溪二先生。往复论质。就考遗事。则有年谱焉。而道德造诣与岁俱深之妙。可验也。有言行录焉。而持论制事。动中礼法之美。可见也。间附公所作诗文仅十篇。虽其绪馀之发。而原本性情。典雅有致。非如词章家浮华雕琢为也。抑细玩之。则一部所录。有可以感可以兴。无非风人之义也。其合族修稧。敦叙伦谊。则伐木棠棣之意也。搆亭竹林。隐居自乐。则泌水考槃之趣也。师友磋切。学问进修。则淇澳抑戒之旨也。其视汗漫篇章。铿锵声律。以夸耀后世之耳目。何如哉。使后之览是录者。知古之君子先德行而后文艺。则是录之有补于世教。不其大欤。旅轩张先生铭公墓曰。不出性分。有为有守。出言有法。行己不苟。斯言也诚信而有徵矣。公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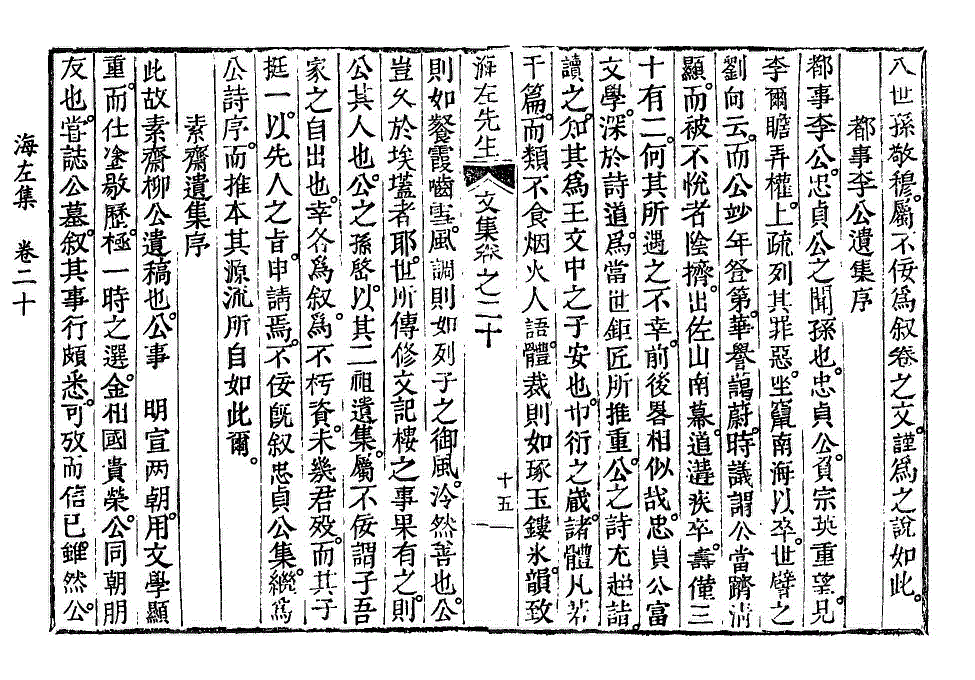 八世孙敬穆。属不佞为叙卷之文。谨为之说如此。
八世孙敬穆。属不佞为叙卷之文。谨为之说如此。都事李公遗集序
都事李公。忠贞公之闻孙也。忠贞公。负宗英重望。见李尔瞻弄权。上疏列其罪恶。坐窜南海以卒。世譬之刘向云。而公妙年登第。华誉蔼蔚。时议谓公当跻清显。而被不悦者阴挤。出佐山南幕。道遘疾卒。寿仅三十有二。何其所遇之不幸。前后略相似哉。忠贞公富文学。深于诗道。为当世钜匠所推重。公之诗尤超诣。读之。知其为王文中之子安也。巾衍之藏。诸体凡若干篇。而类不食烟火人语。体裁则如琢玉镂冰。韵致则如餐霞啮雪。风调则如列子之御风。泠然善也。公岂久于埃壒者耶。世所传修文记楼之事果有之。则公其人也。公之孙𡹘。以其二祖遗集。属不佞谓子吾家之自出也。幸各为叙。为不朽资。未几君殁。而其子挺一。以先人之旨。申请焉。不佞既叙忠贞公集。继为公诗序。而推本其源流所自如此尔。
素斋遗集序
此故素斋柳公遗稿也。公事 明宣两朝。用文学显重。而仕涂扬历。极一时之选。金相国贵荣。公同朝朋友也。尝志公墓。叙其事行颇悉。可考而信已。虽然。公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9L 页
 之所著述。经丙子虏难。荡迭无遗。其九世孙重默。惟湮没是惧。竭诚搜访。得诗文各体若干篇。录为一卷。将乞当世作者弁卷之文。付剞劂为不朽计。不幸重默赍志夭逝。其大人子三甫泣语余曰。愿得子之一言为叙。以成亡子未卒之志。谨按诗凡五十有五篇。清警精赡。有擅场之艺。文凡三十有一篇。浑浑盛世之音。而其议礼一疏及论确前代人哲愚事得失。义理明正。皆可以补世教。尽可传也。集下附录甲契帖及科榜,湖堂选同参人名氏。固若未甚为斯集之重轻。然帖中所载至三十有五人。而多名辈胜流。其并世交游之盛。可知。榜选中诸公。大抵萃一时之精英。而公之名。辄居高等。其望实之隆。为公议所推重。可知。又附公之孙睡庵公遗稿若干。词艺之美。载世彬蔚。又可知。是皆足以垂耀后世之耳目也。子三之意。若以编什之不富为恨。殆不然也。文章要可传而已。乌在其多寡哉。余既感重默为先之诚。而子三之托。其意可悲。故为之叙如此。
之所著述。经丙子虏难。荡迭无遗。其九世孙重默。惟湮没是惧。竭诚搜访。得诗文各体若干篇。录为一卷。将乞当世作者弁卷之文。付剞劂为不朽计。不幸重默赍志夭逝。其大人子三甫泣语余曰。愿得子之一言为叙。以成亡子未卒之志。谨按诗凡五十有五篇。清警精赡。有擅场之艺。文凡三十有一篇。浑浑盛世之音。而其议礼一疏及论确前代人哲愚事得失。义理明正。皆可以补世教。尽可传也。集下附录甲契帖及科榜,湖堂选同参人名氏。固若未甚为斯集之重轻。然帖中所载至三十有五人。而多名辈胜流。其并世交游之盛。可知。榜选中诸公。大抵萃一时之精英。而公之名。辄居高等。其望实之隆。为公议所推重。可知。又附公之孙睡庵公遗稿若干。词艺之美。载世彬蔚。又可知。是皆足以垂耀后世之耳目也。子三之意。若以编什之不富为恨。殆不然也。文章要可传而已。乌在其多寡哉。余既感重默为先之诚。而子三之托。其意可悲。故为之叙如此。石北遗集序
石北申公圣渊既没。余为文而矢哀。为诗而相绋。然尚恨有未尽用情者。圣渊尝谓余曰。苟吾与子之诗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0H 页
 成而将集者。请相为序以相重。使后世知吾与子相知之深。圣渊之殁已二十有四年。而吾亦老且死矣。大惧无以藉手于地下而见圣渊也。乃为之序曰。夫诗难言也。才受之天。学与识在人。三者备而后。诗始成诸。与圣渊游而争长词盟者。盖三四公。而至于才。壹辞推谓不可及。圣渊结发治诗。自国风,离骚,汉魏。下逮盛唐诸名家。含咀英粹。洋溢胸腹而其学蓄。辨雅俗。剂古近。壹归之䡄法而其识精。以是为诗。固至矣而犹未也。尚气者鲜不噪。而乃圣渊。则始微作燕音而卒调之以中声。和雅而鸿鬯也。尚格者鲜不拘。而乃圣渊则如天闲之骏。步骤中规而有昂昂千里之势也。尚采者鲜不秾。而乃圣渊则如泰华之莲。万葩旖旎而浑是真色生香也。以故。其诗声在湖满湖。在洛满洛。一篇出而口相传。遍海内也。诗至此可以已矣。而抑犹未也。夫诗者。心之发也。其心之回直厚薄淑慝。壹于诗而形焉。窃瞷圣渊。惇叙伦物。尤笃故旧。有车笠不忘之谊。喜荐宠后进。有一言之工。辄诩誉稠坐。不容口。其于一切利害得丧。漠然不以为意。盖其心君子人也。故发之为诗者。风调高旷。绝无崎岖龌龊语。圣人以一言。蔽三百篇曰思亡邪。以是而
成而将集者。请相为序以相重。使后世知吾与子相知之深。圣渊之殁已二十有四年。而吾亦老且死矣。大惧无以藉手于地下而见圣渊也。乃为之序曰。夫诗难言也。才受之天。学与识在人。三者备而后。诗始成诸。与圣渊游而争长词盟者。盖三四公。而至于才。壹辞推谓不可及。圣渊结发治诗。自国风,离骚,汉魏。下逮盛唐诸名家。含咀英粹。洋溢胸腹而其学蓄。辨雅俗。剂古近。壹归之䡄法而其识精。以是为诗。固至矣而犹未也。尚气者鲜不噪。而乃圣渊。则始微作燕音而卒调之以中声。和雅而鸿鬯也。尚格者鲜不拘。而乃圣渊则如天闲之骏。步骤中规而有昂昂千里之势也。尚采者鲜不秾。而乃圣渊则如泰华之莲。万葩旖旎而浑是真色生香也。以故。其诗声在湖满湖。在洛满洛。一篇出而口相传。遍海内也。诗至此可以已矣。而抑犹未也。夫诗者。心之发也。其心之回直厚薄淑慝。壹于诗而形焉。窃瞷圣渊。惇叙伦物。尤笃故旧。有车笠不忘之谊。喜荐宠后进。有一言之工。辄诩誉稠坐。不容口。其于一切利害得丧。漠然不以为意。盖其心君子人也。故发之为诗者。风调高旷。绝无崎岖龌龊语。圣人以一言。蔽三百篇曰思亡邪。以是而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0L 页
 蔽圣渊之诗。殆庶几哉。圣渊尝书寓余。以后世孰知海外。有吾二人者为恨。余谓是曷足恨。吾二人。同国而生。并世而相知。又奚论海内外哉。圣渊之诗。无往而无余诗。骊江之诗最奇。而余诗半之。竹西山北之诗最盛。而余诗半之。方其数杯酡颜。分韵命题。毫墨交挥。满纸淋漓。精神声气之会融而为一。则不知余之为圣渊。圣渊之为余也。呜呼。微余。谁当序圣渊集哉。其为文。虽专工不及诗。然亦奇雅有法。读之。知其为圣渊之文也。
蔽圣渊之诗。殆庶几哉。圣渊尝书寓余。以后世孰知海外。有吾二人者为恨。余谓是曷足恨。吾二人。同国而生。并世而相知。又奚论海内外哉。圣渊之诗。无往而无余诗。骊江之诗最奇。而余诗半之。竹西山北之诗最盛。而余诗半之。方其数杯酡颜。分韵命题。毫墨交挥。满纸淋漓。精神声气之会融而为一。则不知余之为圣渊。圣渊之为余也。呜呼。微余。谁当序圣渊集哉。其为文。虽专工不及诗。然亦奇雅有法。读之。知其为圣渊之文也。艮翁集序
艮翁李公既殁之三年。公之馀子廷䄵。负遗集。走岭南将入梓。诸岭南士友之尝慕公风而嘉廷䄵之诚者。颇捐橐以相役。役既讫。属不佞为叙。以不佞与公并世游而相契深也。乃为之叙曰。谭者谓文章与运世盛衰。其言固是矣。而若公有不可以运世局之者。何也。 国家亭午之运。推 明,宣二圣世。乘起而为鸿儒钜匠者林立。其文章闳博渊奥。全受光岳气。何其盛也。嗣是而下二百有馀年。而作者之气寝衰。如五齐之酒去母。愈久而质愈漓。运世使之也。公生而灵识天授。甫七八岁。属语奇警。菊圃,药山诸宿匠。亟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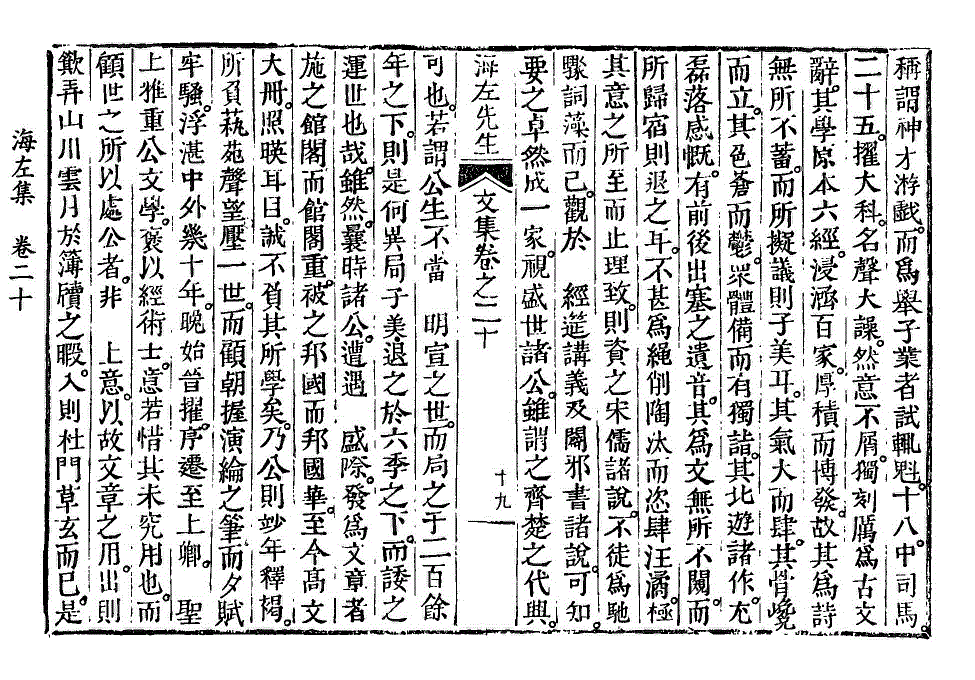 称谓神才游戏。而为举子业者试辄魁。十八。中司马。二十五。擢大科。名声大噪。然意不屑。独刻厉为古文辞。其学原本六经。浸涵百家。厚积而博发。故其为诗无所不蓄。而所拟议则子美耳。其气大而肆。其骨巉而立。其色苍而郁。众体备而有独诣。其北游诸作。尤磊落感慨。有前后出塞之遗音。其为文无所不窥。而所归宿则退之耳。不甚为绳削陶汰而恣肆汪潏。极其意之所至而止理致。则资之宋儒诸说。不徒为驰骤词藻而已。观于 经筵讲义及辟邪书诸说。可知。要之卓然成一家。视盛世诸公。虽谓之齐楚之代兴。可也。若谓公生不当 明宣之世。而局之于二百馀年之下。则是何异局子美,退之于六季之下。而诿之运世也哉。虽然。曩时诸公。遭遇 盛际。发为文章者施之馆阁而馆阁重。被之邦国而邦国华。至今高文大册。照映耳目。诚不负其所学矣。乃公则妙年释褐。所负萟苑声望压一世。而顾朝握演纶之笔而夕赋牢骚。浮湛中外几十年。晚始晋擢。序迁至上卿。 圣上雅重公文学。褒以经术士。意若惜其未究用也。而顾世之所以处公者。非 上意。以故文章之用。出则𥳽弄山川云月于簿牍之暇。入则杜门草玄而已。是
称谓神才游戏。而为举子业者试辄魁。十八。中司马。二十五。擢大科。名声大噪。然意不屑。独刻厉为古文辞。其学原本六经。浸涵百家。厚积而博发。故其为诗无所不蓄。而所拟议则子美耳。其气大而肆。其骨巉而立。其色苍而郁。众体备而有独诣。其北游诸作。尤磊落感慨。有前后出塞之遗音。其为文无所不窥。而所归宿则退之耳。不甚为绳削陶汰而恣肆汪潏。极其意之所至而止理致。则资之宋儒诸说。不徒为驰骤词藻而已。观于 经筵讲义及辟邪书诸说。可知。要之卓然成一家。视盛世诸公。虽谓之齐楚之代兴。可也。若谓公生不当 明宣之世。而局之于二百馀年之下。则是何异局子美,退之于六季之下。而诿之运世也哉。虽然。曩时诸公。遭遇 盛际。发为文章者施之馆阁而馆阁重。被之邦国而邦国华。至今高文大册。照映耳目。诚不负其所学矣。乃公则妙年释褐。所负萟苑声望压一世。而顾朝握演纶之笔而夕赋牢骚。浮湛中外几十年。晚始晋擢。序迁至上卿。 圣上雅重公文学。褒以经术士。意若惜其未究用也。而顾世之所以处公者。非 上意。以故文章之用。出则𥳽弄山川云月于簿牍之暇。入则杜门草玄而已。是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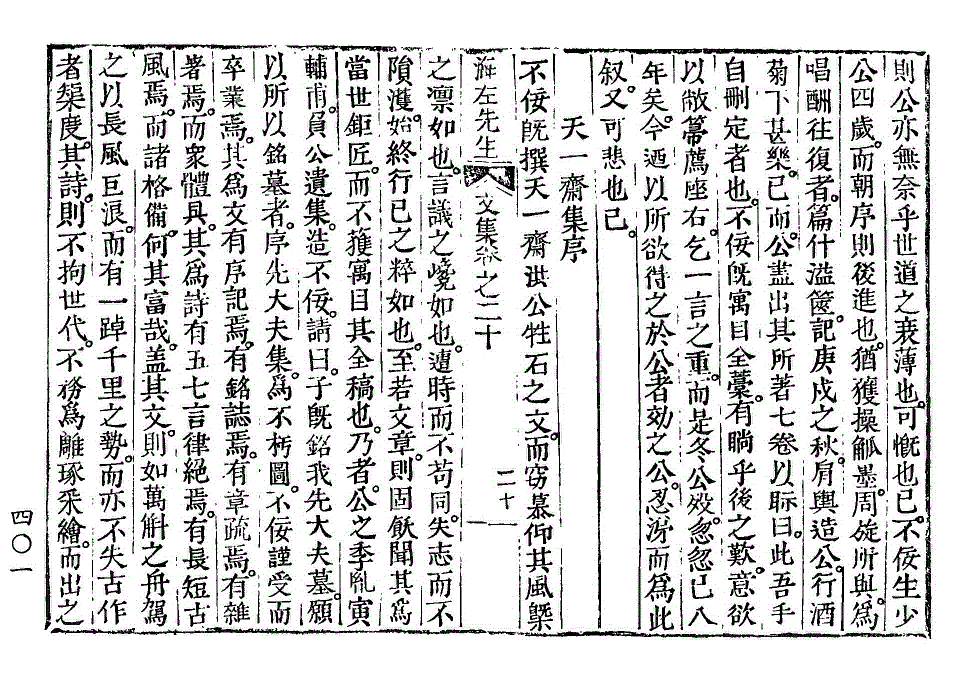 则公亦无奈乎世道之衰薄也。可慨也已。不佞生少公四岁。而朝序则后进也。犹获操觚墨。周旋所与。为唱酬往复者。篇什溢箧。记庚戌之秋。肩舆造公。行酒菊下甚乐。已而。公尽出其所著七卷以视曰。此吾手自删定者也。不佞既寓目全藁。有
则公亦无奈乎世道之衰薄也。可慨也已。不佞生少公四岁。而朝序则后进也。犹获操觚墨。周旋所与。为唱酬往复者。篇什溢箧。记庚戌之秋。肩舆造公。行酒菊下甚乐。已而。公尽出其所著七卷以视曰。此吾手自删定者也。不佞既寓目全藁。有天一斋集序
不佞既撰天一斋洪公牲石之文。而窃慕仰其风槩之凛如也。言议之巉如也。遭时而不苟同。失志而不陨濩。始终行己之粹如也。至若文章。则固饫闻其为当世钜匠。而不获寓目其全稿也。乃者。公之季胤寅辅甫。负公遗集。造不佞。请曰。子既铭我先大夫墓。愿以所以铭墓者。序先大夫集。为不朽图。不佞谨受而卒业焉。其为文有序记焉。有铭志焉。有章疏焉。有杂著焉。而众体具。其为诗有五七言律绝焉。有长短古风焉。而诸格备。何其富哉。盖其文。则如万斛之舟驾之以长风巨浪。而有一踔千里之势。而亦不失古作者矩度。其诗。则不拘世代。不务为雕琢采绘。而出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2H 页
 衽带之间者。典而硕也。涵而肆也。圆而鬯也。而不掩其性情之正。要之为馆阁大手也。使公尽出其所蓄。玉佩琼琚。鸣 国家之盛。则何遽逊当时主文诸公哉。而顾无奈乎朝握演纶之笔而夕赋鵩矣。非厄于时故欤。不佞窃尝谓观人。当于其文章。观文章。当于其气。苏子由称司马子长之文。疏荡有奇气。夫子长。豪杰士也。其视汉廷公卿。如公孙弘辈若无睹。而其史记一部。笔削千百世人物而无难焉。盖气使之也。公擢高第。登显仕。晋涂方辟。而顾负气忼慨。不肯与时俗俯仰。善饮酒引满傲睨。有螟蛉二豪之意。以故读其诗文。旷荡豪逸。泽畔之吟。田居之赋。绝不作憔悴落拓语。其浩气之洋溢胸腹。而发泄于毫墨间者。篇篇虹蜺光也。后之读公集者。可以得公之为人矣。
衽带之间者。典而硕也。涵而肆也。圆而鬯也。而不掩其性情之正。要之为馆阁大手也。使公尽出其所蓄。玉佩琼琚。鸣 国家之盛。则何遽逊当时主文诸公哉。而顾无奈乎朝握演纶之笔而夕赋鵩矣。非厄于时故欤。不佞窃尝谓观人。当于其文章。观文章。当于其气。苏子由称司马子长之文。疏荡有奇气。夫子长。豪杰士也。其视汉廷公卿。如公孙弘辈若无睹。而其史记一部。笔削千百世人物而无难焉。盖气使之也。公擢高第。登显仕。晋涂方辟。而顾负气忼慨。不肯与时俗俯仰。善饮酒引满傲睨。有螟蛉二豪之意。以故读其诗文。旷荡豪逸。泽畔之吟。田居之赋。绝不作憔悴落拓语。其浩气之洋溢胸腹。而发泄于毫墨间者。篇篇虹蜺光也。后之读公集者。可以得公之为人矣。菊庵遗集序
诗固有遇不遇哉。通塞之涂异。而诗随而变。境使之也。夫以贾大夫之少年英妙。身际右文之世。治安一策。惊动汉廷诸公。其文辞何其宏肆也。卒之长沙以后。如鵩鸟吊屈诸作。虽外托恢旷。而其旨实悱恻感慨。盖其所遇之不幸也。近时菊庵李公。天才颖脱。程文诸体俱工。试辄居右。及登大第。声誉蔼蔚。柏梁应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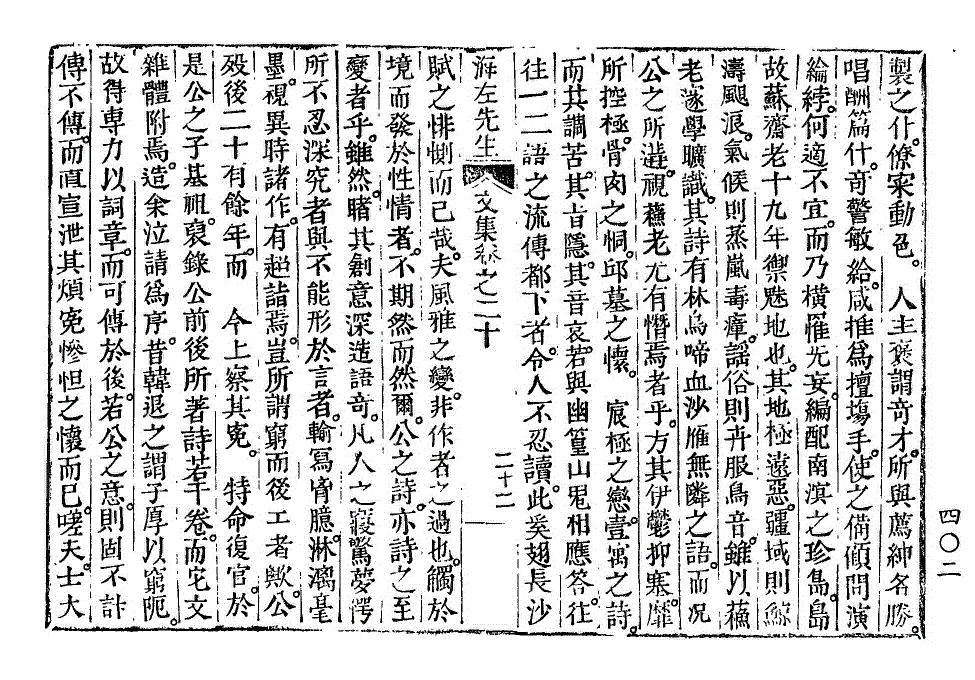 制之什。僚寀动色。 人主褒谓奇才。所与荐绅名胜。唱酬篇什。奇警敏给。咸推为擅场手。使之备顾问演纶綍。何适不宜。而乃横罹无妄。编配南溟之珍岛。岛故苏斋老十九年御魅地也。其地极远恶。疆域则鲸涛飓浪。气候则蒸岚毒瘴。谣俗则卉服鸟音。虽以苏老邃学旷识。其诗有林乌啼血沙雁无邻之语。而况公之所遘。视苏老尤有憯焉者乎。方其伊郁抑塞。靡所控极。骨肉之恫。邱墓之怀。 宸极之恋。壹寓之诗。而其调苦。其旨隐。其音哀。若与幽篁山鬼相应答。往往一二语之流传都下者。令人不忍读。此奚翅长沙赋之悱恻而已哉。夫风雅之变。非作者之过也。触于境而发于性情者。不期然而然尔。公之诗。亦诗之至变者乎。虽然。睹其创意深造语奇。凡人之寝惊梦愕所不忍深究者与不能形于言者。输写胸臆。淋漓毫墨。视异时诸作。有超诣焉。岂所谓穷而后工者欤。公殁后二十有馀年。而 今上察其冤。 特命复官。于是公之子基祖。裒录公前后所著诗若干卷。而它文杂体附焉。造余泣请为序。昔韩退之谓子厚以穷阨。故得专力以词章。而可传于后。若公之意。则固不计传不传。而直宣泄其烦冤惨怛之怀而已。嗟夫。士大
制之什。僚寀动色。 人主褒谓奇才。所与荐绅名胜。唱酬篇什。奇警敏给。咸推为擅场手。使之备顾问演纶綍。何适不宜。而乃横罹无妄。编配南溟之珍岛。岛故苏斋老十九年御魅地也。其地极远恶。疆域则鲸涛飓浪。气候则蒸岚毒瘴。谣俗则卉服鸟音。虽以苏老邃学旷识。其诗有林乌啼血沙雁无邻之语。而况公之所遘。视苏老尤有憯焉者乎。方其伊郁抑塞。靡所控极。骨肉之恫。邱墓之怀。 宸极之恋。壹寓之诗。而其调苦。其旨隐。其音哀。若与幽篁山鬼相应答。往往一二语之流传都下者。令人不忍读。此奚翅长沙赋之悱恻而已哉。夫风雅之变。非作者之过也。触于境而发于性情者。不期然而然尔。公之诗。亦诗之至变者乎。虽然。睹其创意深造语奇。凡人之寝惊梦愕所不忍深究者与不能形于言者。输写胸臆。淋漓毫墨。视异时诸作。有超诣焉。岂所谓穷而后工者欤。公殁后二十有馀年。而 今上察其冤。 特命复官。于是公之子基祖。裒录公前后所著诗若干卷。而它文杂体附焉。造余泣请为序。昔韩退之谓子厚以穷阨。故得专力以词章。而可传于后。若公之意。则固不计传不传。而直宣泄其烦冤惨怛之怀而已。嗟夫。士大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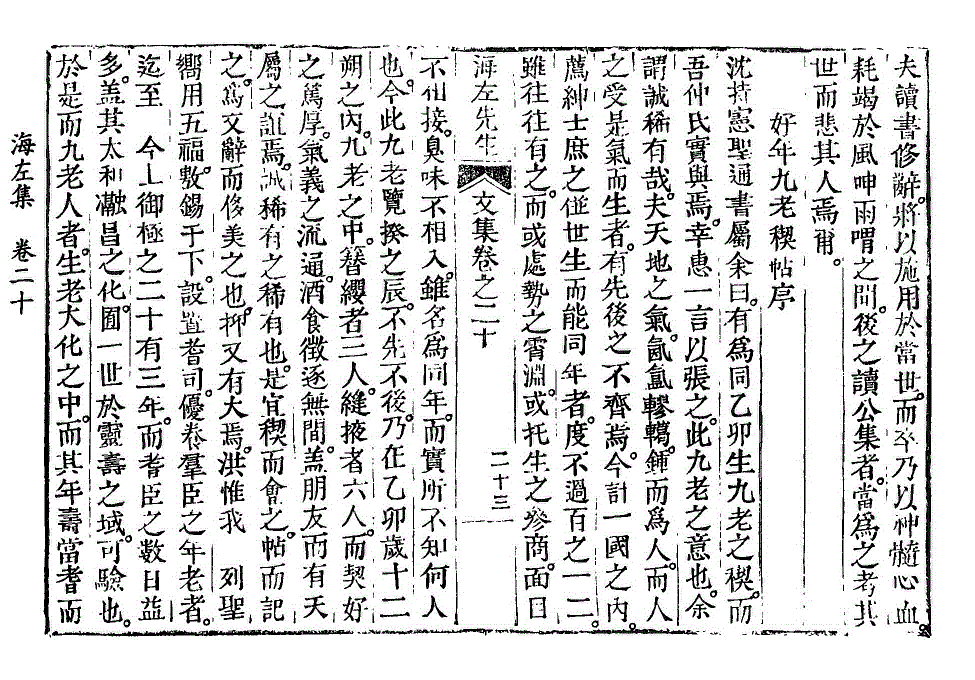 夫读书修辞。将以施用于当世。而卒乃以神髓心血。耗竭于风呻雨喟之间。后之读公集者。当为之考其世而悲其人焉尔。
夫读书修辞。将以施用于当世。而卒乃以神髓心血。耗竭于风呻雨喟之间。后之读公集者。当为之考其世而悲其人焉尔。好年九老稧帖序
沈持宪圣通书属余曰。有为同乙卯生九老之稧。而吾仲氏实与焉。幸惠一言以张之。此九老之意也。余谓诚稀有哉。夫天地之气。氤氲轇轕。钟而为人。而人之受是气而生者。有先后之不齐焉。今计一国之内。荐绅士庶之并世生而能同年者。度不过百之一二。虽往往有之。而或处势之霄渊。或托生之参商。面目不相接。臭味不相入。虽名为同年。而实所不知何人也。今此九老览揆之辰。不先不后。乃在乙卯岁十二朔之内。九老之中。簪缨者三人。缝掖者六人。而契好之笃厚。气义之流通。酒食徵逐无间。盖朋友而有天属之谊焉。诚稀有之稀有也。是宜稧而会之。帖而记之。为文辞而侈美之也。抑又有大焉。洪惟我 列圣向用五福。敷锡于下。设置耆司。优养群臣之年老者。迄至 今上御极之二十有三年。而耆臣之数日益多。盖其太和瀜昌之化。囿一世于灵寿之域。可验也。于是而九老人者。生老大化之中。而其年寿当耆而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3L 页
 耋而耄期。而不知其所极也。此奚徒臣民一家之庆。实东方万世之庆也。矧伏惟我 圣上。乃于乙卯季夏之月。躬奉万年之觞。以献我 慈宫周甲之贺。于是而九老人者。各以是年悬弧之日。受子孙大斗之祝。其上下同乐之盛。有上世气像。而同年稧之名以好年者。盖言九老之生值是年。实与有荣好焉。而蔼然有忠爱之意矣。不佞于此。乌靳为一言以揄扬之哉。
耋而耄期。而不知其所极也。此奚徒臣民一家之庆。实东方万世之庆也。矧伏惟我 圣上。乃于乙卯季夏之月。躬奉万年之觞。以献我 慈宫周甲之贺。于是而九老人者。各以是年悬弧之日。受子孙大斗之祝。其上下同乐之盛。有上世气像。而同年稧之名以好年者。盖言九老之生值是年。实与有荣好焉。而蔼然有忠爱之意矣。不佞于此。乌靳为一言以揄扬之哉。大东韵玉序
韵书之分声配字。协而成章。诚发泄人文之大机籥尔。虽然。字义有限。匠心易局。作者常患不能究极变化。恣肆毫墨。于是有使事庀材之法。而阴氏所撰韵府群玉之书是已。其书蒐猎千古。采蓄百氏。汇而系之百七韵之下。诚韵学之渊海也。虽然。是犹中华之书。而无当于东事。此草涧权公大东韵玉之所繇作也。公蚤游退老之门。盖有薰袭之美。及登朝序。秉持直道。与时龃龉。敛其需世之学而壹寓之是书。法例实仿阴氏。而运用颇出衡量。盖自檀君以后至 国朝。贯穿数千馀岁事实。而旁搜悉摭。山川郡国风谣土物之靡不胪列。而韵书之夏贡也。人道顺逆。国政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4H 页
 善败之靡不纪载。而韵书之鲁史也。公私实录。大小家集。与夫它国文字事涉东方者。靡不考据。而韵书之艺文志也。其于忠臣孝子烈妇三善行。尤致详悉。则表章人纪之微旨可见也。其为世教之补。顾不大欤。若夫词垣之会。拈韵授简。而开卷乍阅。则奇思坌涌。妙境旁会。押韵愈多。而刱语愈新。有滚滚百篇之势。其助发鸿藻之力。何如哉。窃尝论是书之作有三难。东俗荒陋。文献多阙。则采摭之广。一难也。覃思揣摩。积岁成帙。则工力之专。二难也。去冗存醇。默寓劝惩。则见识之精。三难也。苟非聪明博达绝人之艺。则乌能如是哉。是书也当与阴氏之书。互为经纬。而并传天壤间无疑也。粤在 宣庙世。鹤峰金先生拟以一本 进御。锓梓 国学。而值寇难未果。实艺苑之欠事也。公之七世孙进洛。负是书来。属不佞以弁卷之文。傥使是书广布 国中。则不惟嘉惠后学而已。当有以导 宣圣朝右文之化。故不辞而为之序。
善败之靡不纪载。而韵书之鲁史也。公私实录。大小家集。与夫它国文字事涉东方者。靡不考据。而韵书之艺文志也。其于忠臣孝子烈妇三善行。尤致详悉。则表章人纪之微旨可见也。其为世教之补。顾不大欤。若夫词垣之会。拈韵授简。而开卷乍阅。则奇思坌涌。妙境旁会。押韵愈多。而刱语愈新。有滚滚百篇之势。其助发鸿藻之力。何如哉。窃尝论是书之作有三难。东俗荒陋。文献多阙。则采摭之广。一难也。覃思揣摩。积岁成帙。则工力之专。二难也。去冗存醇。默寓劝惩。则见识之精。三难也。苟非聪明博达绝人之艺。则乌能如是哉。是书也当与阴氏之书。互为经纬。而并传天壤间无疑也。粤在 宣庙世。鹤峰金先生拟以一本 进御。锓梓 国学。而值寇难未果。实艺苑之欠事也。公之七世孙进洛。负是书来。属不佞以弁卷之文。傥使是书广布 国中。则不惟嘉惠后学而已。当有以导 宣圣朝右文之化。故不辞而为之序。霁山集序
霁山金公之坐上疏讼师冤而被 谴也。在 英宗二十四年丁巳。其皋复于鵩舍。距丁巳十一年丁卯。人或谓公之疏固是矣。而其于时不可何。乃公之意。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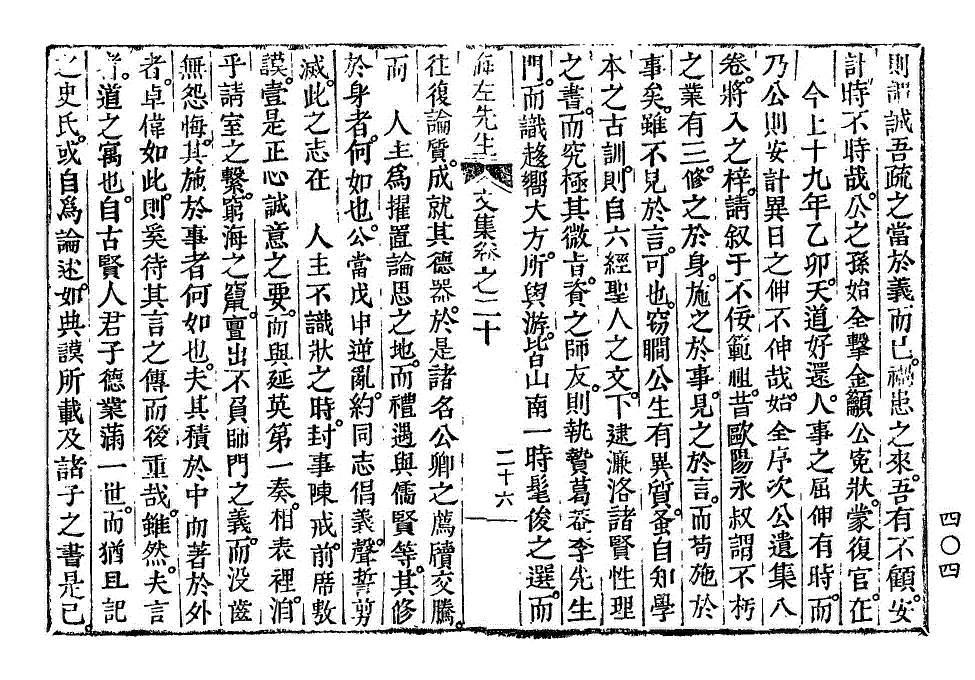 则谓诚吾疏之当于义而已。祸患之来。吾有不顾。安计时不时哉。公之孙始全击金吁公冤状。蒙复官。在 今上十九年乙卯。天道好还。人事之屈伸有时。而乃公则安计异日之伸不伸哉。始全序次公遗集八卷。将入之梓。请叙于不佞范祖。昔欧阳永叔谓不朽之业有三。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而苟施于事矣。虽不见于言。可也。窃瞷公生有异质。蚤自知学本之古训。则自六经圣人之文。下逮濂洛诸贤性理之书。而究极其微旨。资之师友。则执贽葛庵李先生门。而识趍向大方。所与游。皆山南一时髦俊之选。而往复论质。成就其德器。于是诸名公卿之荐牍交腾。而 人主为擢置论思之地。而礼遇与儒贤等。其修于身者。何如也。公当戊申逆乱。约同志倡义。声誓剪灭。此之志在 人主不识状之时。封事陈戒。前席敷谟。壹是正心诚意之要。而与延英第一奏。相表里。洎乎请室之系。穷海之窜。亶出不负师门之义。而没齿无怨悔。其施于事者何如也。夫其积于中而著于外者。卓伟如此。则奚待其言之传而后重哉。虽然。夫言者。道之寓也。自古贤人君子德业满一世。而犹且记之史氏。或自为论述。如典谟所载及诸子之书是已。
则谓诚吾疏之当于义而已。祸患之来。吾有不顾。安计时不时哉。公之孙始全击金吁公冤状。蒙复官。在 今上十九年乙卯。天道好还。人事之屈伸有时。而乃公则安计异日之伸不伸哉。始全序次公遗集八卷。将入之梓。请叙于不佞范祖。昔欧阳永叔谓不朽之业有三。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而苟施于事矣。虽不见于言。可也。窃瞷公生有异质。蚤自知学本之古训。则自六经圣人之文。下逮濂洛诸贤性理之书。而究极其微旨。资之师友。则执贽葛庵李先生门。而识趍向大方。所与游。皆山南一时髦俊之选。而往复论质。成就其德器。于是诸名公卿之荐牍交腾。而 人主为擢置论思之地。而礼遇与儒贤等。其修于身者。何如也。公当戊申逆乱。约同志倡义。声誓剪灭。此之志在 人主不识状之时。封事陈戒。前席敷谟。壹是正心诚意之要。而与延英第一奏。相表里。洎乎请室之系。穷海之窜。亶出不负师门之义。而没齿无怨悔。其施于事者何如也。夫其积于中而著于外者。卓伟如此。则奚待其言之传而后重哉。虽然。夫言者。道之寓也。自古贤人君子德业满一世。而犹且记之史氏。或自为论述。如典谟所载及诸子之书是已。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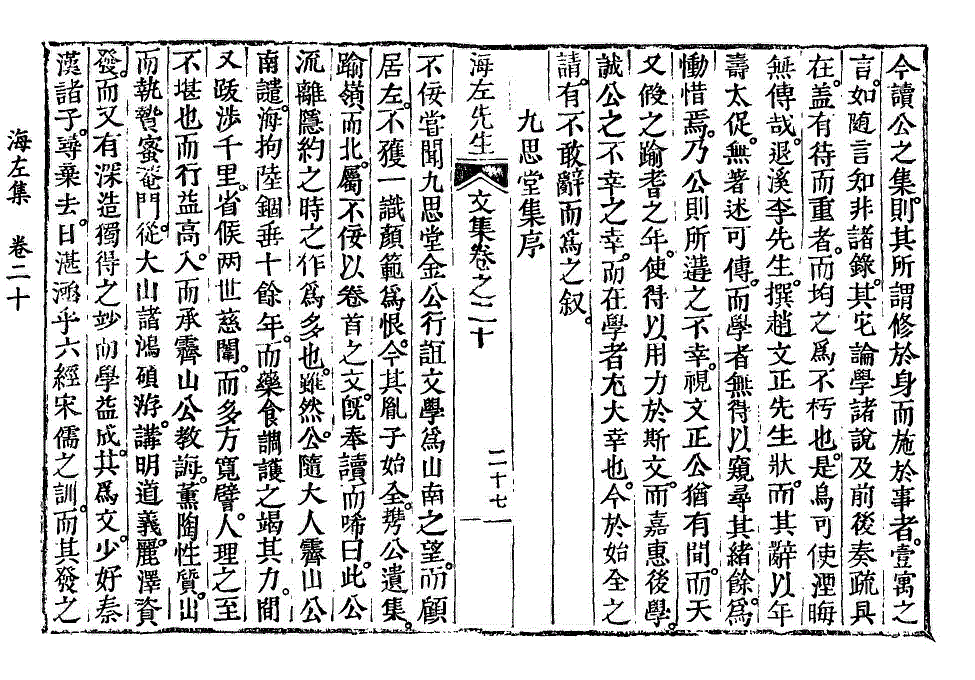 今读公之集。则其所谓修于身而施于事者。壹寓之言。如随言知非诸录。其它论学诸说及前后奏疏具在。盖有待而重者。而均之为不朽也。是乌可使湮晦无传哉。退溪李先生。撰赵文正先生状。而其辞以年寿太促。无著述可传。而学者无得以窥寻其绪馀。为恸惜焉。乃公则所遘之不幸。视文正公犹有间。而天又假之踰耆之年。使得以用力于斯文。而嘉惠后学。诚公之不幸之幸。而在学者尤大幸也。今于始全之请。有不敢辞而为之叙。
今读公之集。则其所谓修于身而施于事者。壹寓之言。如随言知非诸录。其它论学诸说及前后奏疏具在。盖有待而重者。而均之为不朽也。是乌可使湮晦无传哉。退溪李先生。撰赵文正先生状。而其辞以年寿太促。无著述可传。而学者无得以窥寻其绪馀。为恸惜焉。乃公则所遘之不幸。视文正公犹有间。而天又假之踰耆之年。使得以用力于斯文。而嘉惠后学。诚公之不幸之幸。而在学者尤大幸也。今于始全之请。有不敢辞而为之叙。九思堂集序
不佞尝闻九思堂金公行谊文学为山南之望。而顾居左。不获一识颜范为恨。今其胤子始全。携公遗集。踰岭而北。属不佞以卷首之文。既奉读而唏曰。此公流离隐约之时之作为多也。虽然。公随大人霁山公南谴。海拘陆锢垂十馀年。而药食调护之竭其力。间又跋涉千里。省候两世慈闱。而多方宽譬。人理之至不堪也而行益高。入而承霁山公教诲。薰陶性质。出而执贽蜜庵门。从大山诸鸿硕游。讲明道义。丽泽资发。而又有深造独得之妙而学益成。其为文。少好秦汉诸子。寻弃去。日湛涵乎六经宋儒之训。而其发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5L 页
 为著述者。不出性命道德伦常典礼。而曲而鬯也。博而要也。后世道与文歧。修辞者伤藻绘。辞达者病肤率。而乃公则剂而衷之。故要之为贯道之文。而不失作者䡄度也。诗亦典雅清圆。以濂洛之致。本之性情之正。而津津乎其有味也。嗟夫。行高矣学成矣。辅以文术矣。天之赋与公者如此。而卒其所以享之。何其甚畸欤。乙卯冬。始全击金吁霁山公冤。 上特命复官。继下 悯纶。若曰。尔之父祖行谊。予所稔知。而恨不及收用。天道之定。与 圣人之心相会。而绌伸有时哉。人或谓使公而在。当遭时登显。展布其所学否。不佞曰。未可知也。时人之甘心于霁山公者。肠肚相授。如毒虺之不忘螫。公之
为著述者。不出性命道德伦常典礼。而曲而鬯也。博而要也。后世道与文歧。修辞者伤藻绘。辞达者病肤率。而乃公则剂而衷之。故要之为贯道之文。而不失作者䡄度也。诗亦典雅清圆。以濂洛之致。本之性情之正。而津津乎其有味也。嗟夫。行高矣学成矣。辅以文术矣。天之赋与公者如此。而卒其所以享之。何其甚畸欤。乙卯冬。始全击金吁霁山公冤。 上特命复官。继下 悯纶。若曰。尔之父祖行谊。予所稔知。而恨不及收用。天道之定。与 圣人之心相会。而绌伸有时哉。人或谓使公而在。当遭时登显。展布其所学否。不佞曰。未可知也。时人之甘心于霁山公者。肠肚相授。如毒虺之不忘螫。公之乐翁诗藁序
盖余从乐翁游自弱冠时。而其游必于诗。余于翁之诗。始而惊。中而畏。卒之甚悲也。余结发治诗。服习古作者。常谓今之世。未有如古人者。骤见翁诗。则古人也。是以惊。既长。游涂益广。得与当世号能诗者。相上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6H 页
 下。而未有如翁之诗者。是以畏。翁既没。每遇酒赋之会。有时意不适。而思与翁抵掌风雅而不可得。是以甚悲之也。翁长身白面。两眼如星。胸中澹然无一物。故其诗风调清远。得之性情。持论甚亢。谓汉魏六朝盛唐而下亡诗。故其诗古意。得之十九首。赠遗。得之苏李陈。思王记胜。得之谢灵运。近体诸作。得之老杜。而又其天才绝伦。足以济之也。大要存真朴。去雕琢。壹出之高古閒澹。而于山水。尤得意。间为如词如谣如楚人之些者。尤跌宕奇丽可诵。其洒脱而或欠绳削。超诣而或欠结搆。谭者以为疵。而抑不如是。何以见翁诗之异于今人诗哉。翁遇余辄唱酬为乐。人或戏谓余诗优于翁。翁仰而笑。谓翁诗优于余。余故瞪目不答。若不相下者然。余固甘于下翁也。翁行必以诗随。两袖皆诗草。而亦秘不人人视也。尝游汉京。诸少年之浮慕公者。争邀翁谈诗。然能真知翁诗而好之者。亡几。独李先辈芐亭直心公。亟称为希音。而余友石北申圣渊笃好之。翁竟以布衣殁。诗亦佚其十四五。翁之从弟士宗裒录为一卷。而其从侄浚。属余为叙。噫。非余叙翁。谁当叙哉。虽然。是诗将蠹食灰沉败箧中而已耶。抑或有怜而为之梓者耶。未可知也。
下。而未有如翁之诗者。是以畏。翁既没。每遇酒赋之会。有时意不适。而思与翁抵掌风雅而不可得。是以甚悲之也。翁长身白面。两眼如星。胸中澹然无一物。故其诗风调清远。得之性情。持论甚亢。谓汉魏六朝盛唐而下亡诗。故其诗古意。得之十九首。赠遗。得之苏李陈。思王记胜。得之谢灵运。近体诸作。得之老杜。而又其天才绝伦。足以济之也。大要存真朴。去雕琢。壹出之高古閒澹。而于山水。尤得意。间为如词如谣如楚人之些者。尤跌宕奇丽可诵。其洒脱而或欠绳削。超诣而或欠结搆。谭者以为疵。而抑不如是。何以见翁诗之异于今人诗哉。翁遇余辄唱酬为乐。人或戏谓余诗优于翁。翁仰而笑。谓翁诗优于余。余故瞪目不答。若不相下者然。余固甘于下翁也。翁行必以诗随。两袖皆诗草。而亦秘不人人视也。尝游汉京。诸少年之浮慕公者。争邀翁谈诗。然能真知翁诗而好之者。亡几。独李先辈芐亭直心公。亟称为希音。而余友石北申圣渊笃好之。翁竟以布衣殁。诗亦佚其十四五。翁之从弟士宗裒录为一卷。而其从侄浚。属余为叙。噫。非余叙翁。谁当叙哉。虽然。是诗将蠹食灰沉败箧中而已耶。抑或有怜而为之梓者耶。未可知也。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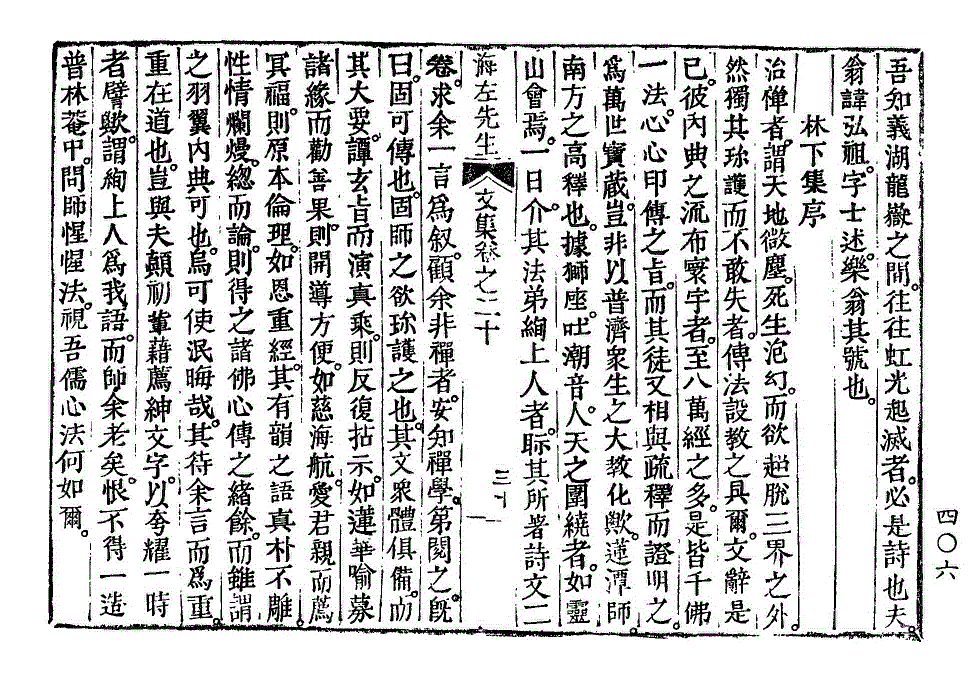 吾知义湖龙岳之间。往往虹光起灭者。必是诗也夫。翁讳弘祖。字士述。乐翁其号也。
吾知义湖龙岳之间。往往虹光起灭者。必是诗也夫。翁讳弘祖。字士述。乐翁其号也。林下集序
治禅者。谓天地微尘。死生泡幻。而欲超脱三界之外。然独其珍护而不敢失者。传法设教之具尔。文辞是已。彼内典之流布寰宇者。至八万经之多。是皆千佛一法。心心印传之旨。而其徒又相与疏释而證明之。为万世宝藏。岂非以普济众生之大教化欤。莲潭师。南方之高释也。据狮座。吐潮音。人天之围绕者。如灵山会焉。一日。介其法弟绚上人者。视其所著诗文二卷。求余一言为叙。顾余非禅者。安知禅学。第阅之。既曰。固可传也。固师之欲珍护之也。其文众体俱备。而其大要。谭玄旨而演真乘。则反复拈示。如莲华喻募诸缘而劝善果。则开导方便。如慈海航。爱君亲而荐冥福。则原本伦理。如恩重经。其有韵之语真朴不雕。性情烂熳。总而论。则得之诸佛心传之绪馀。而虽谓之羽翼内典可也。乌可使泯晦哉。其待余言而为重。重在道也。岂与夫颠初辈藉荐绅文字。以夸耀一时者譬欤。谓绚上人为我语。而师余老矣。恨不得一造普林庵中。问师惺惺法。视吾儒心法何如尔。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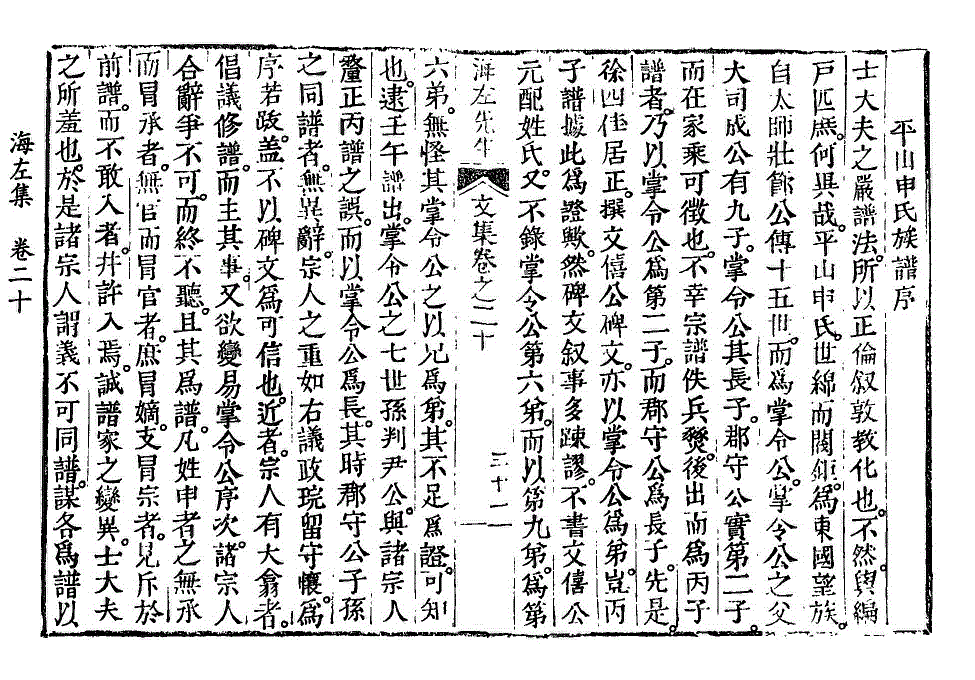 平山申氏族谱序
平山申氏族谱序士大夫之严谱法。所以正伦叙敦教化也。不然。与编户匹庶。何异哉。平山申氏。世绵而阀钜。为东国望族。自太师壮节公传十五世。而为掌令公。掌令公之父大司成公有九子。掌令公其长子。郡守公实第二子。而在家乘可徵也。不幸宗谱佚兵燹。后出而为丙子。谱者。乃以掌令公为第二子。而郡守公为长子。先是。徐四佳居正。撰文僖公碑文。亦以掌令公为弟。岂丙子谱据此为證欤。然碑文叙事多疏谬。不书文僖公元配姓氏。又不录掌令公第六弟。而以第九弟。为第六弟。无怪其掌令公之以兄为弟。其不足为證。可知也。逮壬午谱出。掌令公之七世孙判尹公。与诸宗人釐正丙谱之误。而以掌令公为长。其时郡守公子孙之同谱者。无异辞。宗人之重如右议政琓留守懹。为序若跋。盖不以碑文为可信也。近者。宗人有大翕者。倡议修谱。而主其事。又欲变易掌令公序次。诸宗人合辞争不可。而终不听。且其为谱。凡姓申者之无承而冒承者。无官而冒官者。庶冒嫡。支冒宗者。见斥于前谱。而不敢入者。并许入焉。诚谱家之变异。士大夫之所羞也。于是诸宗人谓义不可同谱。谋各为谱以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7L 页
 传其子孙。以范祖之为申氏外出也。属为序。范祖作而曰。夫掌令公之序次有家乘。又经诸先辈之證正。而壬午谱为定论。今又继而有新谱。无所事乎卞明。顾独有所慨然者。东俗寡陋。士大夫固不能远记其代序。丙谱之作。距掌令公仅六七世。伦序之切近而易明者。莫如亲兄弟。而乃认兄为弟。指支为宗。始而误。中而争。卒之乖离之极。同祖异谱而莫之怪。是不惟申氏之不幸。实世教之不幸也。今按新谱。序昭穆。明本支。严谨而不紊。简洁而不杂。深得谱家正例。后世子孙如欲敦叙本宗辨别伪派。有合谱收族之意。则必于是乎取法焉。故不辞而为之序。
传其子孙。以范祖之为申氏外出也。属为序。范祖作而曰。夫掌令公之序次有家乘。又经诸先辈之證正。而壬午谱为定论。今又继而有新谱。无所事乎卞明。顾独有所慨然者。东俗寡陋。士大夫固不能远记其代序。丙谱之作。距掌令公仅六七世。伦序之切近而易明者。莫如亲兄弟。而乃认兄为弟。指支为宗。始而误。中而争。卒之乖离之极。同祖异谱而莫之怪。是不惟申氏之不幸。实世教之不幸也。今按新谱。序昭穆。明本支。严谨而不紊。简洁而不杂。深得谱家正例。后世子孙如欲敦叙本宗辨别伪派。有合谱收族之意。则必于是乎取法焉。故不辞而为之序。大司成柳公遗集序
此故大司成柳公遗集也。公生 文宗二年壬申。 成宗三年壬辰。中进士。二十年己酉。擢大科。 中宗七年壬申卒。立朝凡二十馀年。而官至国子长。处昏朝则直声动一世。际昌辰则用经术道德。辅导 圣学。师表后进。何其盛欤。其著述巾衍之藏。当有以补益世教者。而不幸遘兵燹荡然。是为子孙之恨。然不佞则谓公之可传者。有不待此而信者。何也。昔唐时直臣。推魏郑公一人。而其大略有史氏之纪而已。未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8H 页
 尝自为论著以求显于后世。宋儒性命之学。自濂溪周夫子始。而其见于文字者。秖太极而已。而自程朱诸贤皆推尊之。蔚为儒宗。盖公之大节。有晋川君姜公浑之重。而为之铭公墓。其铭曰。谔谔疏论。烈烈风霜。白日雷霆。杖窜遐方。人皆震惧。公笑而当。其言照人耳目。公尝撰大学十箴,性理撮要二书。进御经筵。而其渊源之正。造诣之奥。往往与退溪李先生理气说暗契。 中庙览之嘉奖。亟命印布。公又以谚文释经书旨义。嘉惠后学。而 当宁尝问筵臣曰。作经书谚解者。谁也。筵臣以公对。 教曰。尽钜儒也。若使二书进经 天览。则其表章而褒扬之者。当何如也。假令公之全藁尚完。岂有出于二书之外者哉。是乌足为子孙恨。公之八世孙剡。将以公集付剞劂为永久图。抵书不佞。求为卷首一言。不佞既以传世之重。不在著述多寡告之。因为叙。而抑是集。奚待不佞言而信。
尝自为论著以求显于后世。宋儒性命之学。自濂溪周夫子始。而其见于文字者。秖太极而已。而自程朱诸贤皆推尊之。蔚为儒宗。盖公之大节。有晋川君姜公浑之重。而为之铭公墓。其铭曰。谔谔疏论。烈烈风霜。白日雷霆。杖窜遐方。人皆震惧。公笑而当。其言照人耳目。公尝撰大学十箴,性理撮要二书。进御经筵。而其渊源之正。造诣之奥。往往与退溪李先生理气说暗契。 中庙览之嘉奖。亟命印布。公又以谚文释经书旨义。嘉惠后学。而 当宁尝问筵臣曰。作经书谚解者。谁也。筵臣以公对。 教曰。尽钜儒也。若使二书进经 天览。则其表章而褒扬之者。当何如也。假令公之全藁尚完。岂有出于二书之外者哉。是乌足为子孙恨。公之八世孙剡。将以公集付剞劂为永久图。抵书不佞。求为卷首一言。不佞既以传世之重。不在著述多寡告之。因为叙。而抑是集。奚待不佞言而信。真乐堂遗集序
尚论古人有术。章显则徵其事业。隐约则考其文辞而已。然斯人也弗施于世。无事业可徵。躬修默行。弗肯以言语表见。而无文辞可考。则观于其师友间推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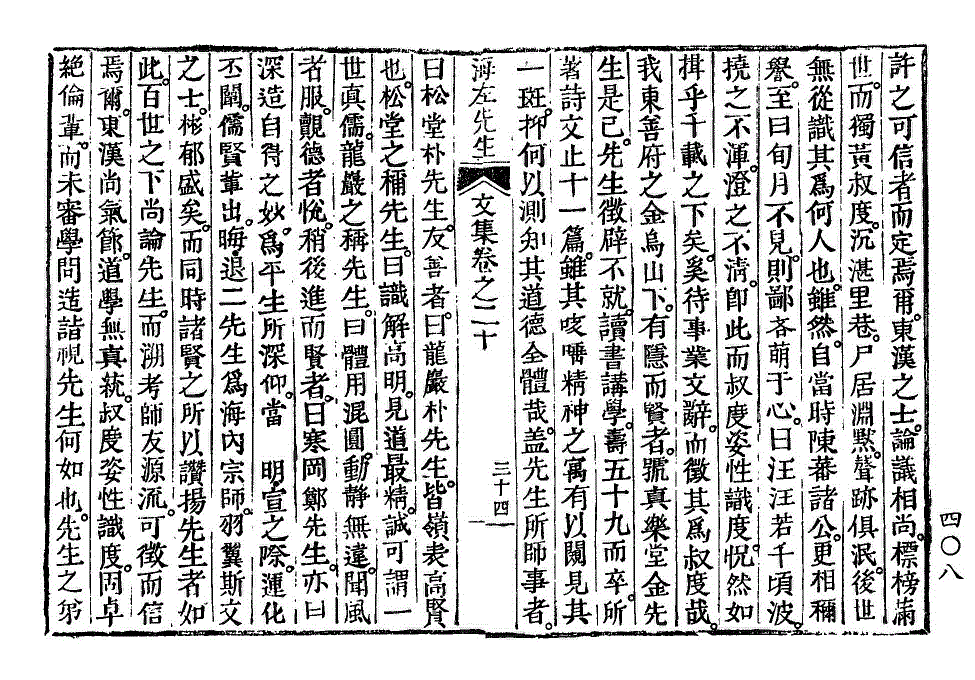 许之可信者而定焉尔。东汉之士。论议相尚。标榜满世。而独黄叔度。沉湛里巷。尸居渊默。声迹俱泯。后世无从识其为何人也。虽然。自当时陈蕃诸公。更相称誉。至曰旬月不见。则鄙吝萌于心。曰汪汪若千顷波。挠之不浑。澄之不清。即此而叔度姿性识度。恍然如揖乎千载之下矣。奚待事业文辞。而徵其为叔度哉。我东善府之金乌山下。有隐而贤者。号真乐堂金先生是已。先生徵辟不就。读书讲学。寿五十九而卒。所著诗文止十一篇。虽其咳唾精神之寓有以窥见其一斑。抑何以测知其道德全体哉。盖先生所师事者。曰松堂朴先生。友善者。曰龙岩朴先生。皆岭表高贤也。松堂之称先生。曰识解高明。见道最精。诚可谓一世真儒。龙岩之称先生。曰体用混圆。动静无违。闻风者服。觌德者悦。稍后进而贤者。曰寒冈郑先生。亦曰深造自得之妙。为平生所深仰。当 明,宣之际。运化丕阐。儒贤辈出。晦,退二先生为海内宗师。羽翼斯文之士。彬郁盛矣。而同时诸贤之所以赞扬先生者如此。百世之下尚论先生。而溯考师友源流。可徵而信焉尔。东汉尚气节。道学无真统。叔度姿性识度。固卓绝伦辈。而未审学问造诣视先生何如也。先生之弟
许之可信者而定焉尔。东汉之士。论议相尚。标榜满世。而独黄叔度。沉湛里巷。尸居渊默。声迹俱泯。后世无从识其为何人也。虽然。自当时陈蕃诸公。更相称誉。至曰旬月不见。则鄙吝萌于心。曰汪汪若千顷波。挠之不浑。澄之不清。即此而叔度姿性识度。恍然如揖乎千载之下矣。奚待事业文辞。而徵其为叔度哉。我东善府之金乌山下。有隐而贤者。号真乐堂金先生是已。先生徵辟不就。读书讲学。寿五十九而卒。所著诗文止十一篇。虽其咳唾精神之寓有以窥见其一斑。抑何以测知其道德全体哉。盖先生所师事者。曰松堂朴先生。友善者。曰龙岩朴先生。皆岭表高贤也。松堂之称先生。曰识解高明。见道最精。诚可谓一世真儒。龙岩之称先生。曰体用混圆。动静无违。闻风者服。觌德者悦。稍后进而贤者。曰寒冈郑先生。亦曰深造自得之妙。为平生所深仰。当 明,宣之际。运化丕阐。儒贤辈出。晦,退二先生为海内宗师。羽翼斯文之士。彬郁盛矣。而同时诸贤之所以赞扬先生者如此。百世之下尚论先生。而溯考师友源流。可徵而信焉尔。东汉尚气节。道学无真统。叔度姿性识度。固卓绝伦辈。而未审学问造诣视先生何如也。先生之弟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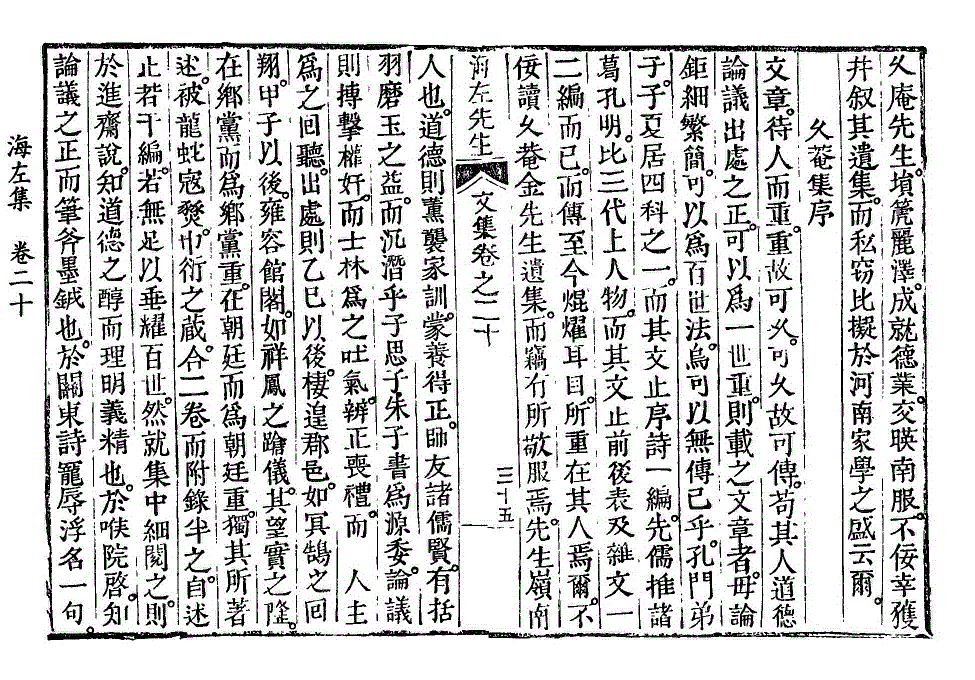 久庵先生。埙篪丽泽。成就德业。交映南服。不佞幸获并叙其遗集。而私窃比拟于河南家学之盛云尔。
久庵先生。埙篪丽泽。成就德业。交映南服。不佞幸获并叙其遗集。而私窃比拟于河南家学之盛云尔。久庵集序
文章。待人而重。重故可久。可久故可传。苟其人道德论议出处之正。可以为一世重。则载之文章者。毋论钜细繁简。可以为百世法。乌可以无传已乎。孔门弟子。子夏居四科之一。而其文止序诗一编。先儒推诸葛孔明。比三代上人物。而其文止前后表及杂文一二编而已。而传至今焜耀耳目。所重在其人焉尔。不佞读久庵金先生遗集。而窃有所敬服焉。先生岭南人也。道德则薰袭家训。蒙养得正。师友诸儒贤。有括羽磨玉之益。而沉潜乎子思子,朱子书为源委。论议则搏击权奸。而士林为之吐气。辨正丧礼。而 人主为之回听。出处则乙巳以后。栖遑郡邑。如冥鹄之回翔。甲子以后。雍容馆阁。如祥凤之跄仪。其望实之隆。在乡党而为乡党重。在朝廷而为朝廷重。独其所著述。被龙蛇寇燹。巾衍之藏。合二卷而附录半之。自述止若干编。若无足以垂耀百世。然就集中细阅之。则于进斋说。知道德之醇而理明义精也。于喉院启。知论议之正而笔斧墨钺也。于关东诗宠辱浮名一句。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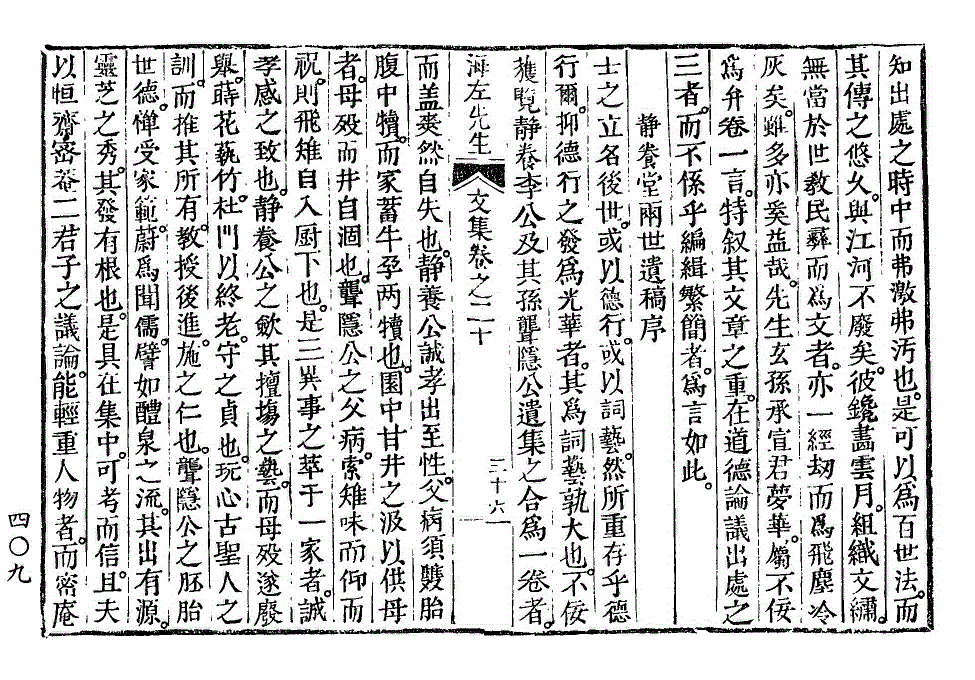 知出处之时中而弗激弗污也。是可以为百世法。而其传之悠久。与江河不废矣。彼镵画云月。组织文绣。无当于世教民彝而为文者。亦一经劫而为飞尘冷灰矣。虽多亦奚益哉。先生玄孙承宣君梦华。属不佞为弁卷一言。特叙其文章之重。在道德论议出处之三者。而不系乎编缉繁简者。为言如此。
知出处之时中而弗激弗污也。是可以为百世法。而其传之悠久。与江河不废矣。彼镵画云月。组织文绣。无当于世教民彝而为文者。亦一经劫而为飞尘冷灰矣。虽多亦奚益哉。先生玄孙承宣君梦华。属不佞为弁卷一言。特叙其文章之重。在道德论议出处之三者。而不系乎编缉繁简者。为言如此。静养堂两世遗稿序
士之立名后世。或以德行。或以词艺。然所重存乎德行尔。抑德行之发为光华者。其为词艺孰大也。不佞获览静养李公及其孙聋隐公遗集之合为一卷者。而盖爽然自失也。静养公诚孝出至性。父病须双胎腹中犊。而家蓄牛孕两犊也。园中甘井之汲以供母者。母殁而井自涸也。聋隐公之父病。索雉味而仰而祝。则飞雉自入厨下也。是三异事之萃于一家者。诚孝感之致也。静养公之敛其擅场之艺。而母殁遂废举。莳花蓺竹。杜门以终老。守之贞也。玩心古圣人之训。而推其所有。教授后进。施之仁也。聋隐公之胚胎世德。禅受家范。蔚为闻儒。譬如醴泉之流。其出有源。灵芝之秀。其发有根也。是具在集中。可考而信。且夫以恒斋,密庵二君子之议论。能轻重人物者。而密庵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0H 页
 公之撰静养遗事。赞扬备至。而證以恒斋公之言曰。静养公吾宗大老。叔世仪范。其它同时朋友之重而论聋隐公曰。某之节行高致。隐于文章。此足以恃而千古矣。二公雅不喜词章末技。然往往兴象之所感。触。性灵之所陶写。形于赋咏者。各若干篇。而要皆有德之言也。深之则发泄理窟。浅之则牢笼物态。宛然有濂洛遗响。有非词人墨客雕花镂叶之比而已。亦足以附而传也。静养公之玄孙(缺)。徵不佞为卷首一言。谨叙二公之先德行而后词艺者为说。使后之览者。知所择焉尔。
公之撰静养遗事。赞扬备至。而證以恒斋公之言曰。静养公吾宗大老。叔世仪范。其它同时朋友之重而论聋隐公曰。某之节行高致。隐于文章。此足以恃而千古矣。二公雅不喜词章末技。然往往兴象之所感。触。性灵之所陶写。形于赋咏者。各若干篇。而要皆有德之言也。深之则发泄理窟。浅之则牢笼物态。宛然有濂洛遗响。有非词人墨客雕花镂叶之比而已。亦足以附而传也。静养公之玄孙(缺)。徵不佞为卷首一言。谨叙二公之先德行而后词艺者为说。使后之览者。知所择焉尔。星隐孙公遗集序
心术之淑慝。莫逃于文辞之发。譬如悬镜而照。物无遁形。不可诬也。上世勿论。丽时李相国奎报著述。号最赡博。顷刻千言。然谄附权奸。败名行而饕禄利。故其诗文淫巧卑浊。无士夫气。视益牧诸公。品格犹奴隶耳。余读密城星隐孙公遗集。而窃耸异也。集凡诗文杂体为一卷。而其诗雪洁冰清。类不食烟火人语。一再讽之。泠然若骖鸾鹤而上太清。翩翩仙化也。就考公平生志行。则抱贞守真。持身若处子。当甲戌世局嬗改。南中有观势向背者。说公曰。少变初志。进取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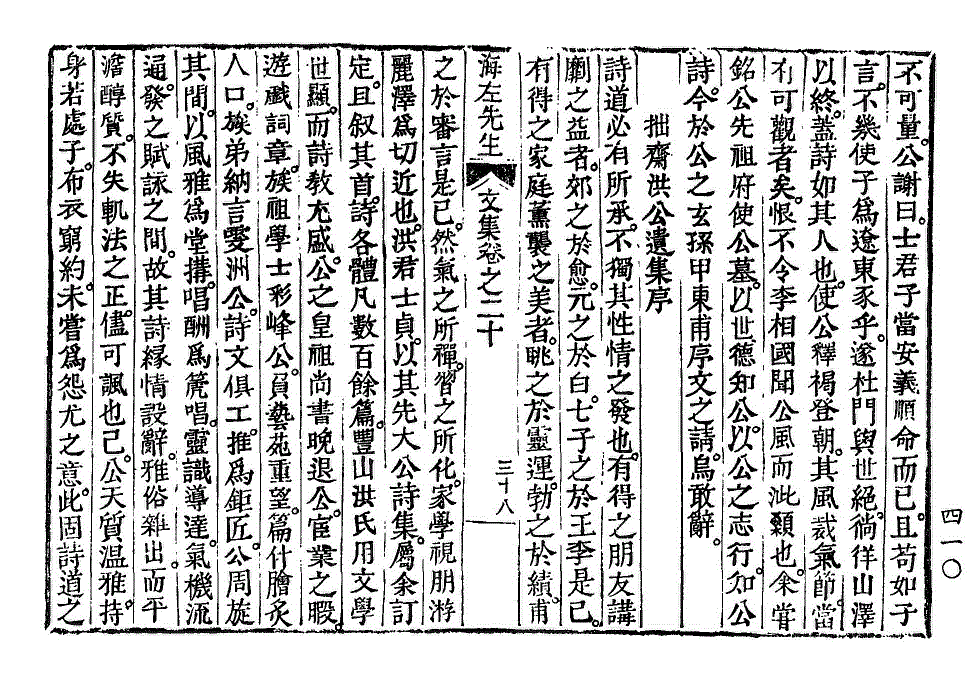 不可量。公谢曰。士君子当安义顺命而已。且苟如子言。不几使子为辽东豕乎。遂杜门与世绝。徜徉山泽以终。盖诗如其人也。使公释褐登朝。其风裁气节。当有可观者矣。恨不令李相国闻公风而泚颡也。余尝铭公先祖府使公墓。以世德知公。以公之志行。知公诗。今于公之玄孙甲东甫序文之请。乌敢辞。
不可量。公谢曰。士君子当安义顺命而已。且苟如子言。不几使子为辽东豕乎。遂杜门与世绝。徜徉山泽以终。盖诗如其人也。使公释褐登朝。其风裁气节。当有可观者矣。恨不令李相国闻公风而泚颡也。余尝铭公先祖府使公墓。以世德知公。以公之志行。知公诗。今于公之玄孙甲东甫序文之请。乌敢辞。拙斋洪公遗集序
诗道必有所承。不独其性情之发也。有得之朋友讲劘之益者。郊之于愈。元之于白。七子之于王李是已。有得之家庭薰袭之美者。眺之于灵运。勃之于绩。甫之于审言是已。然气之所禅。习之所化。家学视朋游丽泽为切近也。洪君士贞。以其先大公诗集。属余订定。且叙其首。诗各体凡数百馀篇。丰山洪氏用文学世显。而诗教尤盛。公之皇祖尚书晚退公。宦业之暇。游戏词章。族祖学士彩峰公。负艺苑重望。篇什脍炙人口。族弟纳言雯洲公。诗文俱工。推为钜匠。公周旋其间。以风雅为堂搆。唱酬为篪唱。灵识导达。气机流通。发之赋咏之间。故其诗缘情设辞。雅俗杂出。而平澹醇质。不失䡄法之正。尽可讽也已。公天质温雅。持身若处子。布衣穷约。未尝为怨尤之意。此固诗道之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1H 页
 根据。而若其受授绳尺。润饰华藻。则得之父兄宗党之内者为多。奚啻友道偲切之助而已哉。后之读公诗者。不问可知为洪氏集矣。
根据。而若其受授绳尺。润饰华藻。则得之父兄宗党之内者为多。奚啻友道偲切之助而已哉。后之读公诗者。不问可知为洪氏集矣。耘谷集序
当国初鼎革之际。为王氏立节。推郑圃隐,吉冶隐,元耘谷三先生。尤卓伟。譬殷之三仁焉。虽然。圃隐元老也。佩宗社安危。国亡与亡。则以一死任纲常之重。冶隐犹是门下注书也。见邦箓将迄。天命有归。力不能救。则逴然长逝。甘作金乌逸民。盖二先生自靖之义。皎如日星。国史书之。后世诵之。而其迹显。至若元先生。特前朝一进士耳。未尝立王氏之朝。食王氏之禄。而龙兴圣人。即同学旧契也。乘运攀附。为佐命勋臣。夫谁曰不可。而特以世禄之裔。义不事二姓。匿伏大山嵁岩之中。与木石同老。而其迹微而隐。其处义视二先生为尤难。嗟夫。今读先生遗集。可以窥测其心事矣。其讴吟咏叹。与樵歌渔唱错出。而有时感念宗国。输写胸臆。直指则悲愤慷慨。婉寄则徘徊掩抑。宛然有麦秀采薇之遗音。盖先生之意。欲袭之巾衍。秘之石室。不欲散落人间。是不徒隐其迹。而又将隐其辞。故曰其处义。视二先生为尤难已。虽然。天下之理。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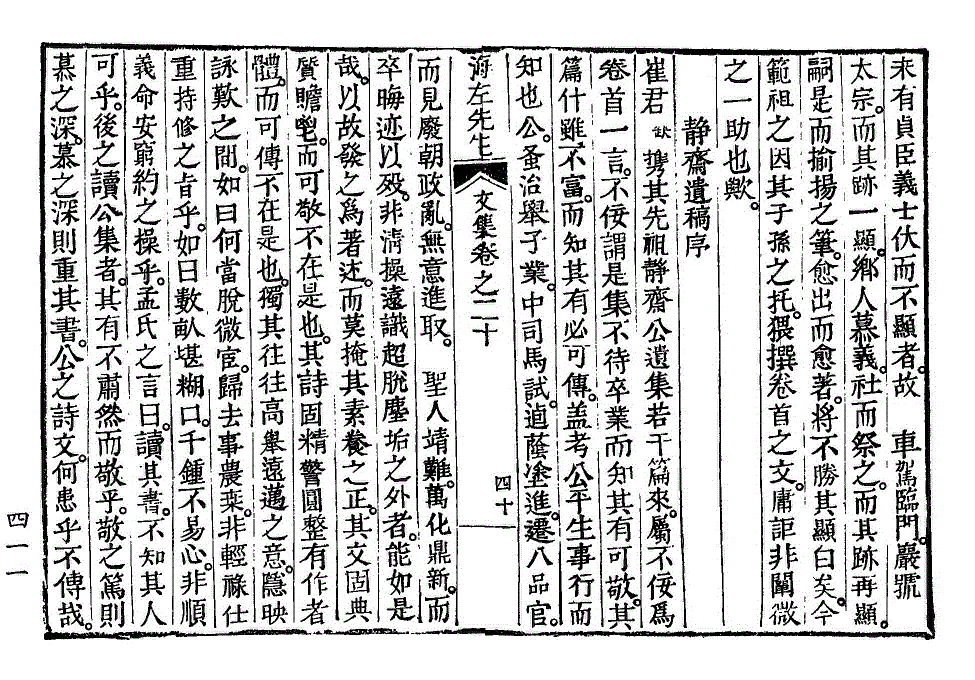 未有贞臣义士伏而不显者。故 车驾临门。岩号 太宗。而其迹一显。乡人慕义。社而祭之。而其迹再显。嗣是而揄扬之笔。愈出而愈著。将不胜其显白矣。今范祖之因其子孙之托。猥撰卷首之文。庸讵非阐微之一助也欤。
未有贞臣义士伏而不显者。故 车驾临门。岩号 太宗。而其迹一显。乡人慕义。社而祭之。而其迹再显。嗣是而揄扬之笔。愈出而愈著。将不胜其显白矣。今范祖之因其子孙之托。猥撰卷首之文。庸讵非阐微之一助也欤。静斋遗稿序
崔君(缺)携其先祖静斋公遗集若干篇来。属不佞为卷首一言。不佞谓是集不待卒业而知其有可敬。其篇什虽不富。而知其有必可传。盖考公平生事行而知也公。蚤治举子业。中司马试。逌荫涂进。迁八品官。而见废朝政乱。无意进取。 圣人靖难。万化鼎新。而卒晦迹以殁。非清操远识超脱尘垢之外者。能如是哉。以故发之为著述。而莫掩其素养之正。其文固典质赡鬯。而可敬不在是也。其诗固精警圆整有作者体。而可传不在是也。独其往往高举远迈之意。隐映咏叹之间。如曰何当脱微宦。归去事农桑。非轻禄仕重持修之旨乎。如曰数亩堪糊口。千钟不易心。非顺义命安穷约之操乎。孟氏之言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后之读公集者。其有不肃然而敬乎。敬之笃则慕之深。慕之深则重其书。公之诗文。何患乎不传哉。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2H 页
 不佞既撰崔氏谱序。而详识其世德。自侍中公至观察公三四钜公尤显重。而公能服习先训。继述家声。毋论著述之有亡。其志行足以传后世。而况辅以文艺之美者哉。语(缺)甫亟录是集。毋久作巾衍藏。
不佞既撰崔氏谱序。而详识其世德。自侍中公至观察公三四钜公尤显重。而公能服习先训。继述家声。毋论著述之有亡。其志行足以传后世。而况辅以文艺之美者哉。语(缺)甫亟录是集。毋久作巾衍藏。忠州崔氏族谱序
分身之祖。虽远不可忘。受氏之地。虽久不可去。此人道之常也。虽然。掌族之法废。而私家载籍疏略。鲜能远记其代序。支派分而流转无常。子孙或不识其所自出之乡。此不祥之甚。而东俗为尤甚尔。不佞观于忠州崔氏之族。而窃耸异焉。崔氏起罗季。迄 国朝。自始祖凡二十馀传。而卜世绵。间出达官钜人。若丽之门下侍中宝文阁提学。 国朝之观察使诸公尤著显。而积累之盛。可知。受籍在忠州。上世衣冠之庄附焉。子孙之环州治而居者百馀家。而死徒不出乡。合族敦宗之美。又可知。旧有谱经兵燹荡佚。宗人合议作新谱。辨昭穆。明宗支。颇详谨。请序于不佞。为永久图。不佞念士大夫门户兴替。系子孙贤不肖。苟能述先训。敦族谊。相勉为孝悌仁厚之行。则其家岂有不昌大者乎。崔氏之谱一阅。知某为昭某为穆。某宗分某支。而戚疏无间。则讵不蔼然生敦睦之心乎。再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412L 页
 阅。知某祖葬于斯。某祖葬于彼。警咳若承。则讵不油然起爱慕之诚乎。崔氏子孙。岁时拜于墓。退而合席于宗子之堂。序长少。列笾豆。讲先世之徽猷。叙天伦之乐事。则毓和气。储吉祥。而讵不为昌大门户之兆也乎。是谱也不徒为崔氏世法。其为风化之补不少尔。遂为之序。
阅。知某祖葬于斯。某祖葬于彼。警咳若承。则讵不油然起爱慕之诚乎。崔氏子孙。岁时拜于墓。退而合席于宗子之堂。序长少。列笾豆。讲先世之徽猷。叙天伦之乐事。则毓和气。储吉祥。而讵不为昌大门户之兆也乎。是谱也不徒为崔氏世法。其为风化之补不少尔。遂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