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x 页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序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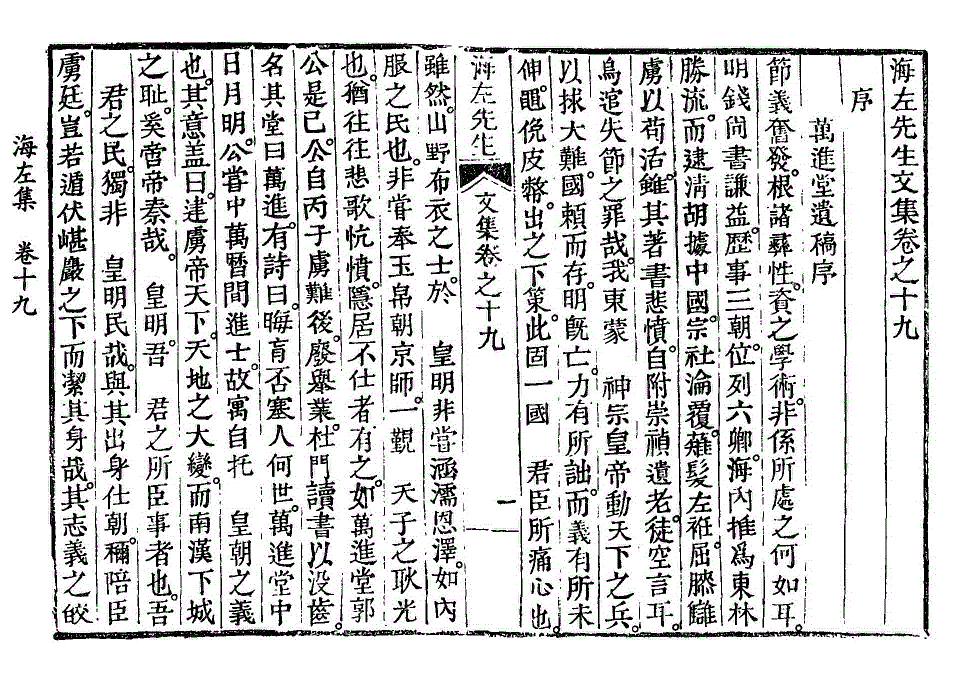 万进堂遗稿序
万进堂遗稿序节义奋发。根诸彝性。资之学术。非系所处之何如耳。明钱尚书谦益。历事三朝。位列六卿。海内推为东林胜流。而逮清胡据中国。宗社沦覆。薙发左衽。屈膝雠虏以苟活。虽其著书悲愤。自附崇祯遗老。徒空言耳。乌逭失节之罪哉。我东蒙 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以救大难。国赖而存。明既亡。力有所诎。而义有所未伸。黾俛皮币。出之下策。此固一国 君臣所痛心也。虽然。山野布衣之士。于 皇明非尝涵濡恩泽。如内服之民也。非尝奉玉帛朝京师。一觐 天子之耿光也。犹往往悲歌忼愤。隐居不仕者有之。如万进堂郭公是已。公自丙子虏难后。废举业。杜门读书以没齿。名其堂曰万进。有诗曰。晦盲否塞人何世。万进堂中日月明。公尝中万历间进士。故寓自托 皇朝之义也。其意盖曰。建虏帝天下。天地之大变。而南汉下城之耻。奚啻帝秦哉。 皇明。吾 君之所臣事者也。吾 君之民。独非 皇明民哉。与其出身仕朝。称陪臣虏廷。岂若遁伏嵁岩之下而洁其身哉。其志义之皎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1L 页
 厉。气节之卓烈。求之当世。廑一二数也。岂非秉彝之性。弗挠弗汨。直遂其所赋之天。故能如此哉。当时主和诸公。亦同有此性。不可谓全昧义利之辨。而惟安 君父保宗社是急。其势不得不讲究权宜。以制一时之变。至若草野之士。则弗然修身善道。知经常。不知有权变。要使天下后世。知三韩有此义理。则其发诸中而为持论处义。宜乎其伉爽也。公之先大抵多伟人。而至叔父忘忧公。当壬辰难。倡义击贼。佐成中恢之烈。母李夫人杀身殉节。㫌其闾。其家庭授受。用节义为世训。而公又博洽经史。研究性理。有践履之实。则其担纲常于一身。树风教于万世者。盖有素讲而然也。嗟夫。贪生忘义。在中朝之世臣。抗节扶纲。出东表之匹士。但问彝性之存丧。学术之有亡而已。乌论夫夷夏内外之尔殊哉。公之曾孙祯垕。袖公遗集录事行及诗文若干来。属不佞为一言。谨读其序记论史诸作。理明词鬯。可见其所存。然此公绪馀之发。故特举其大者。为言如此。
厉。气节之卓烈。求之当世。廑一二数也。岂非秉彝之性。弗挠弗汨。直遂其所赋之天。故能如此哉。当时主和诸公。亦同有此性。不可谓全昧义利之辨。而惟安 君父保宗社是急。其势不得不讲究权宜。以制一时之变。至若草野之士。则弗然修身善道。知经常。不知有权变。要使天下后世。知三韩有此义理。则其发诸中而为持论处义。宜乎其伉爽也。公之先大抵多伟人。而至叔父忘忧公。当壬辰难。倡义击贼。佐成中恢之烈。母李夫人杀身殉节。㫌其闾。其家庭授受。用节义为世训。而公又博洽经史。研究性理。有践履之实。则其担纲常于一身。树风教于万世者。盖有素讲而然也。嗟夫。贪生忘义。在中朝之世臣。抗节扶纲。出东表之匹士。但问彝性之存丧。学术之有亡而已。乌论夫夷夏内外之尔殊哉。公之曾孙祯垕。袖公遗集录事行及诗文若干来。属不佞为一言。谨读其序记论史诸作。理明词鬯。可见其所存。然此公绪馀之发。故特举其大者。为言如此。棠溪遗稿序
不佞结发治文辞。猥尝从当世秇苑诸君子游。其最相善相得甚驩者。曰石北申圣渊暨棠溪金公是已。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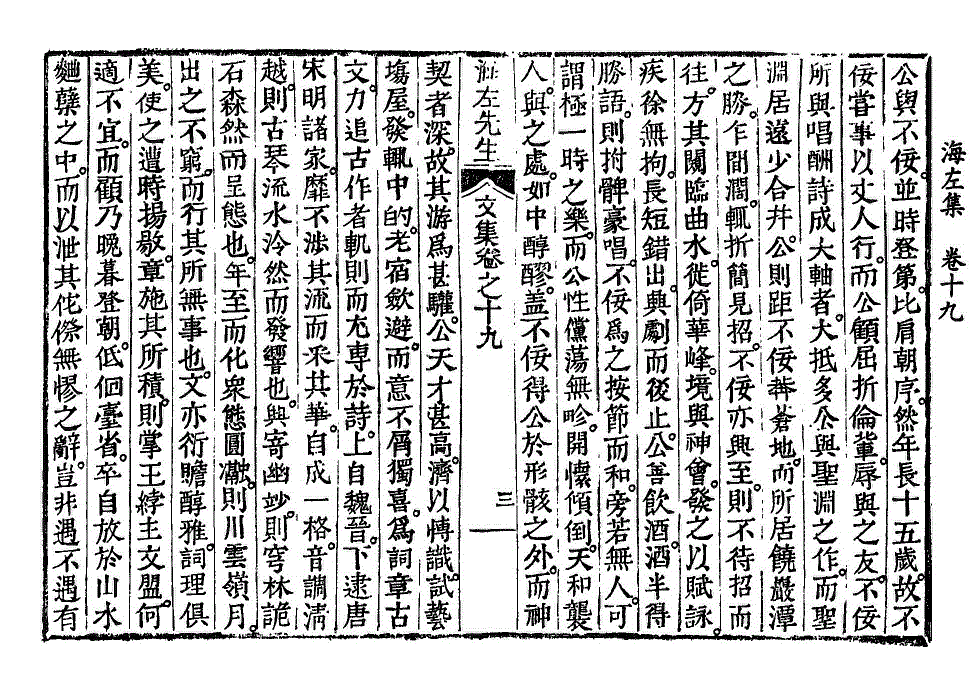 公与不佞。并时登第。比肩朝序。然年长十五岁。故不佞尝事以丈人行。而公顾屈折伦辈。辱与之友。不佞所与唱酬诗成大轴者。大抵多公与圣渊之作。而圣渊居远少合并。公则距不佞莽苍地。而所居饶岩潭之胜。乍间阔。辄折简见招。不佞亦兴至。则不待招而往。方其窥临曲水。徙倚华峰。境与神会。发之以赋咏。疾徐无拘。长短错出。兴剧而后止。公善饮酒。酒半得胜语。则拊髀豪唱。不佞为之按节而和。旁若无人。可谓极一时之乐。而公性傥荡无畛。开怀倾倒。天和袭人。与之处。如中醇醪。盖不佞得公于形骸之外。而神契者深。故其游为甚驩。公天才甚高。济以博识。试艺场屋。发辄中的。老宿敛避。而意不屑独喜。为词章古文。力追古作者轨则而尤专于诗。上自魏晋。下逮唐宋明诸家。靡不涉其流而采其华。自成一格。音调清越。则古琴流水泠然而发响也。兴寄幽妙。则穹林诡石森然而呈态也。年至而化众态圆瀜。则川云岭月。出之不穷。而行其所无事也。文亦衍赡醇雅。词理俱美。使之遭时扬扬。章施其所积。则掌王綍主文盟。何适不宜。而顾乃晚暮登朝。低佪台省。卒自放于山水曲蘖之中。而以泄其佗傺无憀之辞。岂非遇不遇有
公与不佞。并时登第。比肩朝序。然年长十五岁。故不佞尝事以丈人行。而公顾屈折伦辈。辱与之友。不佞所与唱酬诗成大轴者。大抵多公与圣渊之作。而圣渊居远少合并。公则距不佞莽苍地。而所居饶岩潭之胜。乍间阔。辄折简见招。不佞亦兴至。则不待招而往。方其窥临曲水。徙倚华峰。境与神会。发之以赋咏。疾徐无拘。长短错出。兴剧而后止。公善饮酒。酒半得胜语。则拊髀豪唱。不佞为之按节而和。旁若无人。可谓极一时之乐。而公性傥荡无畛。开怀倾倒。天和袭人。与之处。如中醇醪。盖不佞得公于形骸之外。而神契者深。故其游为甚驩。公天才甚高。济以博识。试艺场屋。发辄中的。老宿敛避。而意不屑独喜。为词章古文。力追古作者轨则而尤专于诗。上自魏晋。下逮唐宋明诸家。靡不涉其流而采其华。自成一格。音调清越。则古琴流水泠然而发响也。兴寄幽妙。则穹林诡石森然而呈态也。年至而化众态圆瀜。则川云岭月。出之不穷。而行其所无事也。文亦衍赡醇雅。词理俱美。使之遭时扬扬。章施其所积。则掌王綍主文盟。何适不宜。而顾乃晚暮登朝。低佪台省。卒自放于山水曲蘖之中。而以泄其佗傺无憀之辞。岂非遇不遇有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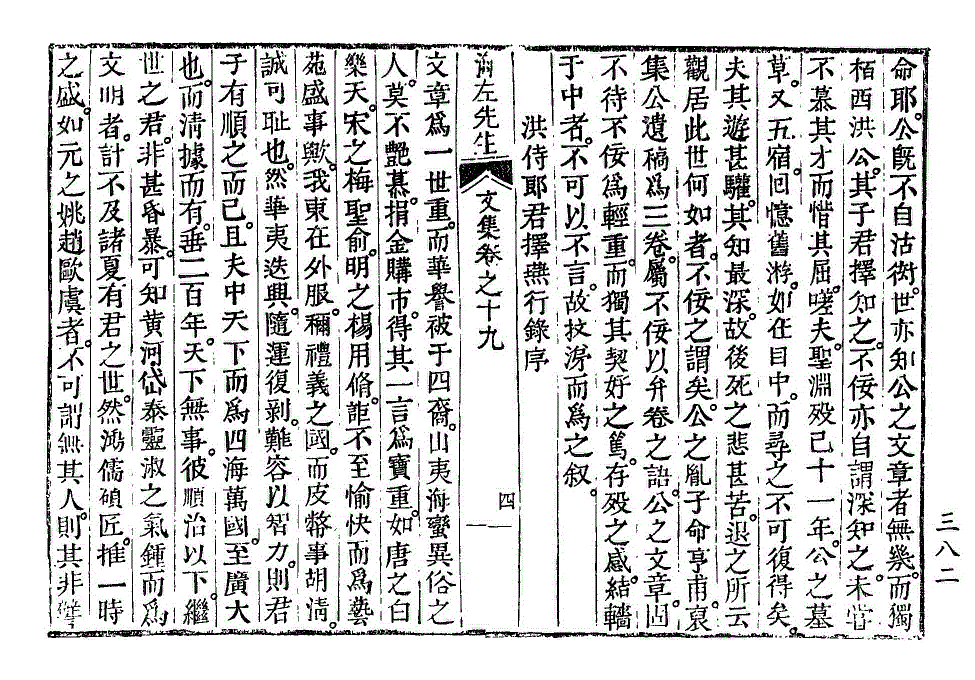 命耶。公既不自沽衒。世亦知公之文章者无几。而独柏西洪公。其子君择知之。不佞亦自谓深知之。未尝不慕其才而惜其屈。嗟夫。圣渊殁已十一年。公之墓草。又五宿。回忆旧游。如在目中。而寻之不可复得矣。夫其游甚驩。其知最深。故后死之悲甚苦。退之所云观居此世何如者。不佞之谓矣。公之胤子命亨甫。裒集公遗稿为三卷。属不佞以弁卷之语。公之文章。固不待不佞为轻重。而独其契好之笃。存殁之感。结轖于中者。不可以不言。故抆涕而为之叙。
命耶。公既不自沽衒。世亦知公之文章者无几。而独柏西洪公。其子君择知之。不佞亦自谓深知之。未尝不慕其才而惜其屈。嗟夫。圣渊殁已十一年。公之墓草。又五宿。回忆旧游。如在目中。而寻之不可复得矣。夫其游甚驩。其知最深。故后死之悲甚苦。退之所云观居此世何如者。不佞之谓矣。公之胤子命亨甫。裒集公遗稿为三卷。属不佞以弁卷之语。公之文章。固不待不佞为轻重。而独其契好之笃。存殁之感。结轖于中者。不可以不言。故抆涕而为之叙。洪侍郎君择燕行录序
文章为一世重。而华誉被于四裔。山夷海蛮异俗之人。莫不艳慕。捐金购市。得其一言为宝重。如唐之白乐天。宋之梅圣俞。明之杨用脩。讵不至愉快而为艺苑盛事欤。我东在外服。称礼义之国。而皮币事胡清。诚可耻也。然华夷迭兴。随运复剥。难容以智力。则君子有顺之而已。且夫中天下而为四海万国。至广大也。而清据而有。垂二百年。天下无事。彼顺治以下。继世之君。非甚昏暴。可知黄河,岱泰灵淑之气钟而为文明者。计不及诸夏有君之世。然鸿儒硕匠。推一时之盛。如元之姚,赵,欧,虞者。不可谓无其人。则其非譬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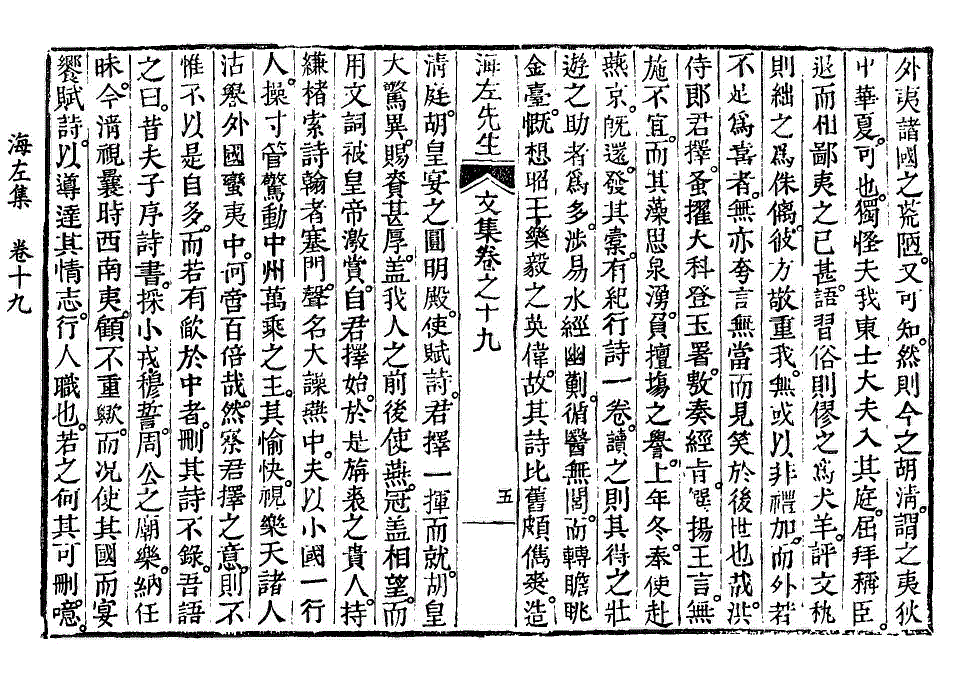 外夷诸国之荒陋。又可知。然则今之胡清。谓之夷狄中华夏。可也。独怪夫我东士大夫入其庭。屈拜称臣。退而相鄙夷之已甚。语习俗则僇之为犬羊。评文秇则绌之为侏𠌯。彼方敬重我。无或以非礼加。而外若不足为喜者。无亦夸言无当而见笑于后世也哉。洪侍郎君择。蚤擢大科登玉署。敷奏经旨。▦扬王言。无施不宜。而其藻思泉涌。负擅场之誉。上年冬。奉使赴燕京。既还。发其橐。有纪行诗一卷。读之则其得之壮游之助者为多。涉易水经幽蓟。循医无闾。而转瞻眺金台。慨想昭王,乐毅之英伟。故其诗比旧颇俊爽。造清庭。胡皇宴之圆明殿。使赋诗。君择一挥而就。胡皇大惊异。赐赉甚厚。盖我人之前后使燕。冠盖相望。而用文词被皇帝激赏。自君择始。于是旃裘之贵人。持缣楮索诗翰者塞门。声名大噪燕中。夫以小国一行人。操寸管惊动中州万乘之主。其愉快。视乐天诸人沽誉外国蛮夷中。何啻百倍哉。然察君择之意。则不惟不以是自多。而若有欿于中者。删其诗不录。吾语之曰。昔夫子序诗书。采小戎,穆誓。周公之庙乐。纳任昧。今清视曩时西南夷。顾不重欤。而况使其国而宴飨赋诗。以导达其情志。行人职也。若之何其可删。噫。
外夷诸国之荒陋。又可知。然则今之胡清。谓之夷狄中华夏。可也。独怪夫我东士大夫入其庭。屈拜称臣。退而相鄙夷之已甚。语习俗则僇之为犬羊。评文秇则绌之为侏𠌯。彼方敬重我。无或以非礼加。而外若不足为喜者。无亦夸言无当而见笑于后世也哉。洪侍郎君择。蚤擢大科登玉署。敷奏经旨。▦扬王言。无施不宜。而其藻思泉涌。负擅场之誉。上年冬。奉使赴燕京。既还。发其橐。有纪行诗一卷。读之则其得之壮游之助者为多。涉易水经幽蓟。循医无闾。而转瞻眺金台。慨想昭王,乐毅之英伟。故其诗比旧颇俊爽。造清庭。胡皇宴之圆明殿。使赋诗。君择一挥而就。胡皇大惊异。赐赉甚厚。盖我人之前后使燕。冠盖相望。而用文词被皇帝激赏。自君择始。于是旃裘之贵人。持缣楮索诗翰者塞门。声名大噪燕中。夫以小国一行人。操寸管惊动中州万乘之主。其愉快。视乐天诸人沽誉外国蛮夷中。何啻百倍哉。然察君择之意。则不惟不以是自多。而若有欿于中者。删其诗不录。吾语之曰。昔夫子序诗书。采小戎,穆誓。周公之庙乐。纳任昧。今清视曩时西南夷。顾不重欤。而况使其国而宴飨赋诗。以导达其情志。行人职也。若之何其可删。噫。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3L 页
 皇明天子当阳。玉帛修觐。退与其贤大夫唱酬。为朝天录。何可复得。盖亦彼此一时也。
皇明天子当阳。玉帛修觐。退与其贤大夫唱酬。为朝天录。何可复得。盖亦彼此一时也。文粹历选序
文章之变。随运世升降。势使然也。醇漓厚薄。精粗深浅。所造意设辞。代异而人殊。然善为文者。皆取而为吾用。而不病其为异也。天地之运。在虞夏商周之际。至隆昌也。周室陵夷。五霸擅征伐。骎骎叔季也。七雄起而彊弱相食。伦纲堕地。乱之极也。汉兴上文学。然政杂王霸。视三古。弗啻下也。即形之为文辞者可验已。典谟诰训。圣人之文。日月之丽天乎。丘明之史。羽翼麟经。管晏诸子。咸有论述。要之尚辞而夸。务功而卑。文之杂者乎。阴阳,捭阖,驵侩之说。莫甚于仪,秦。蔑礼法。崇虚无。放言不忌。莫甚于庄,列。文之裂者乎。迁,固迭兴。史法乃备。仲舒,杨雄。号为儒雅。揆之道德。犹是文之未醇者乎。此之谓文章盛衰。系于运世升降。而难容以人力者也。虽然。若曰文之不轨于圣人之道者。放绝而勿取乎。则诚不知文者也。夫道存乎内。而为宰者正。则文亡邪也。孔子生春秋时。其文春秋也。道存焉。故孔子之文也。孟子生战国时。其文战国也。道存焉。故孟子之文也。故善为文者。本原六经圣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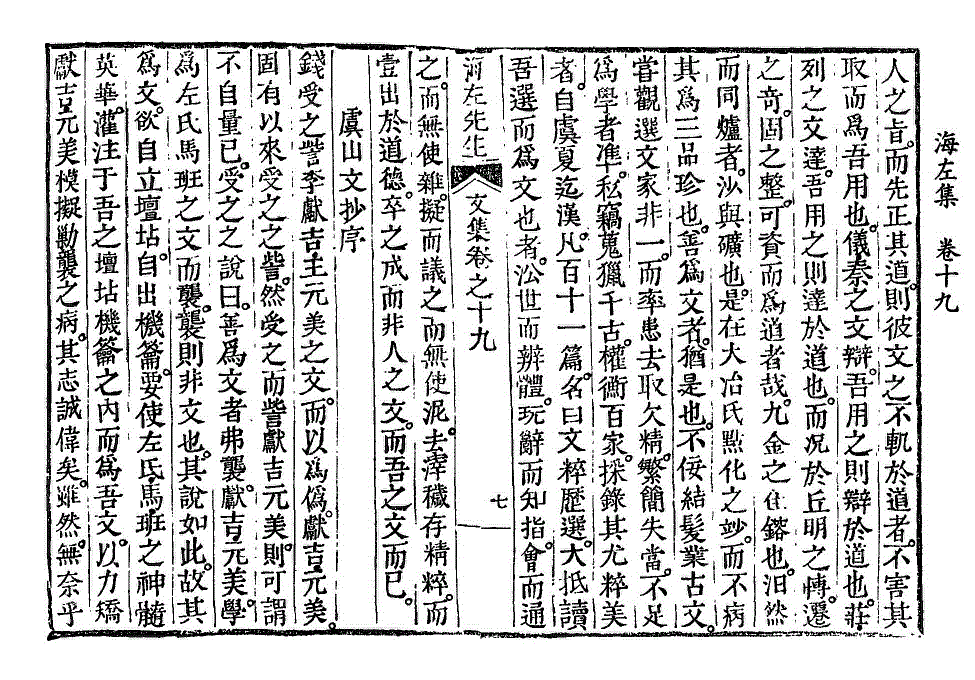 人之旨。而先正其道。则彼文之不轨于道者。不害其取而为吾用也。仪,秦之文辩。吾用之则辩于道也。庄,列之文达。吾用之则达于道也。而况于丘明之博。迁之奇。固之整。可资而为道者哉。九金之在镕也。汨然而同炉者。沙与矿也。是在大冶氏点化之妙。而不病其为三品珍也。善为文者。犹是也。不佞结发业古文。尝观选文家非一。而率患去取欠精。繁简失当。不足为学者准。私窃蒐猎千古。权衡百家。采录其尤粹美者。自虞夏迄汉。凡百十一篇。名曰文粹历选。大抵读吾选而为文也者。沿世而辨体。玩辞而知指。会而通之。而无使杂。拟而议之而无使泥。去滓秽存精粹。而壹出于道德。卒之成而非人之文。而吾之文而已。
人之旨。而先正其道。则彼文之不轨于道者。不害其取而为吾用也。仪,秦之文辩。吾用之则辩于道也。庄,列之文达。吾用之则达于道也。而况于丘明之博。迁之奇。固之整。可资而为道者哉。九金之在镕也。汨然而同炉者。沙与矿也。是在大冶氏点化之妙。而不病其为三品珍也。善为文者。犹是也。不佞结发业古文。尝观选文家非一。而率患去取欠精。繁简失当。不足为学者准。私窃蒐猎千古。权衡百家。采录其尤粹美者。自虞夏迄汉。凡百十一篇。名曰文粹历选。大抵读吾选而为文也者。沿世而辨体。玩辞而知指。会而通之。而无使杂。拟而议之而无使泥。去滓秽存精粹。而壹出于道德。卒之成而非人之文。而吾之文而已。虞山文抄序
钱受之訾李献吉,王元美之文。而以为伪。献吉,元美。固有以来受之之訾。然受之而訾献吉元美。则可谓不自量已。受之之说曰。善为文者弗袭。献吉,元美。学为左氏,马,班之文而袭。袭则非文也。其说如此。故其为文。欲自立坛坫。自出机籥。要使左氏,马,班之神髓英华。灌注于吾之坛坫机籥之内而为吾文。以力矫献吉,元美模拟剿袭之病。其志诚伟矣。虽然。无奈乎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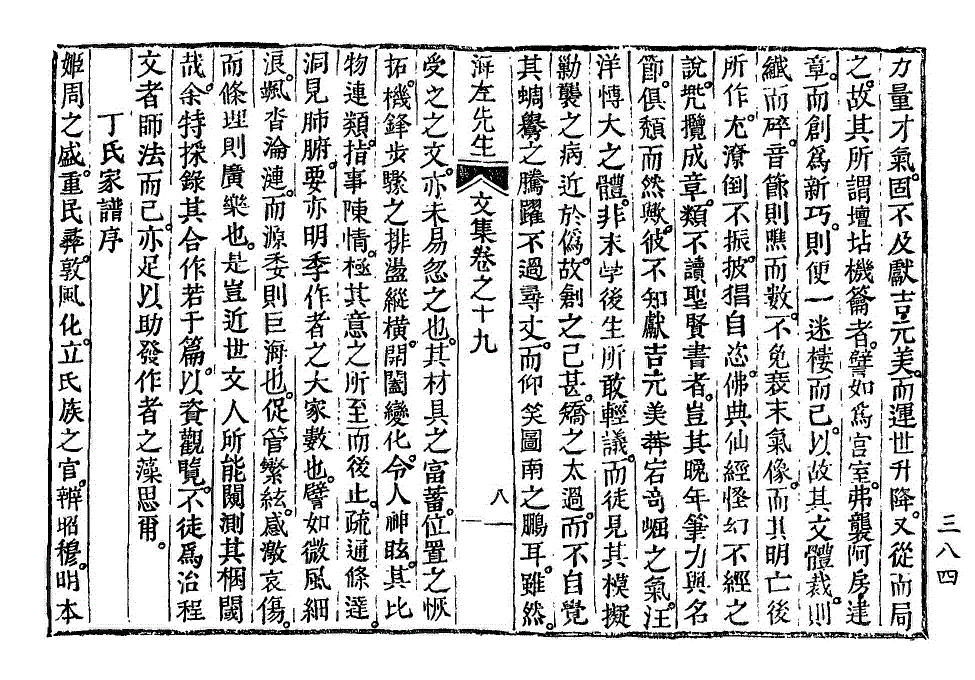 力量才气。固不及献吉,元美。而运世升降。又从而局之。故其所谓坛坫机籥者。譬如为宫室。弗袭阿房,建章。而创为新巧。则使一迷楼而已。以故其文体裁。则纤而碎。音节则噍而数。不免衰末气像。而其明亡后所作。尤潦倒不振。披猖自恣。佛典仙经怪幻不经之说。兜揽成章。类不读圣贤书者。岂其晚年笔力与名节。俱颓而然欤。彼不知献吉,元美莽宕奇崛之气。汪洋博大之体。非末学后生所敢轻议。而徒见其模拟剿袭之病近于伪。故创之已甚。矫之太过。而不自觉其蜩鸴之腾跃不过寻丈。而仰笑图南之鹏耳。虽然。受之之文。亦未易忽之也。其材具之富蓄。位置之恢拓。机锋步骤之排荡纵横。开阖变化。令人神眩。其比物连类。指事陈情。极其意之所至而后止。疏通条达。洞见肺腑。要亦明季作者之大家数也。譬如微风细浪。飒沓沦涟。而源委则巨海也。促管繁弦。感激哀伤。而条理则广乐也。是岂近世文人所能窥测其梱阈哉。余特采录其合作若干篇。以资观览。不徒为治程文者师法而已。亦足以助发作者之藻思尔。
力量才气。固不及献吉,元美。而运世升降。又从而局之。故其所谓坛坫机籥者。譬如为宫室。弗袭阿房,建章。而创为新巧。则使一迷楼而已。以故其文体裁。则纤而碎。音节则噍而数。不免衰末气像。而其明亡后所作。尤潦倒不振。披猖自恣。佛典仙经怪幻不经之说。兜揽成章。类不读圣贤书者。岂其晚年笔力与名节。俱颓而然欤。彼不知献吉,元美莽宕奇崛之气。汪洋博大之体。非末学后生所敢轻议。而徒见其模拟剿袭之病近于伪。故创之已甚。矫之太过。而不自觉其蜩鸴之腾跃不过寻丈。而仰笑图南之鹏耳。虽然。受之之文。亦未易忽之也。其材具之富蓄。位置之恢拓。机锋步骤之排荡纵横。开阖变化。令人神眩。其比物连类。指事陈情。极其意之所至而后止。疏通条达。洞见肺腑。要亦明季作者之大家数也。譬如微风细浪。飒沓沦涟。而源委则巨海也。促管繁弦。感激哀伤。而条理则广乐也。是岂近世文人所能窥测其梱阈哉。余特采录其合作若干篇。以资观览。不徒为治程文者师法而已。亦足以助发作者之藻思尔。丁氏家谱序
姬周之盛。重民彝。敦风化。立氏族之官。辨昭穆。明本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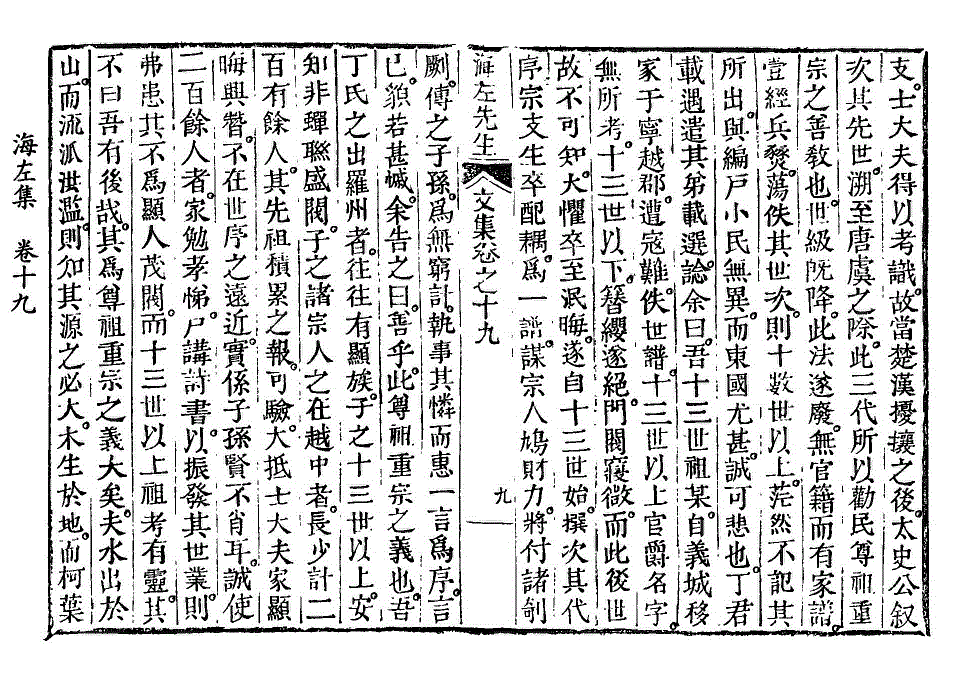 支。士大夫得以考识。故当楚汉扰攘之后。太史公叙次其先世。溯至唐虞之际。此三代所以劝民尊祖重宗之善教也。世级既降。此法遂废。无官籍而有家谱。壹经兵燹。荡佚其世次。则十数世以上。茫然不记其所出。与编户小民无异。而东国尤甚。诚可悲也。丁君载遇遣其弟载选。谂余曰。吾十三世祖某。自义城移家于宁越郡。遭寇难。佚世谱。十三世以上官爵名字。无所考。十三世以下。簪缨遂绝。门阀寝微。而此后世故不可知。大惧卒至泯晦。遂自十三世始。撰次其代序宗支生卒配耦。为一谱。谋宗人鸠财力。将付诸剞劂。传之子孙。为无穷计。执事其怜而惠一言为序。言已。貌若甚戚。余告之曰。善乎。此尊祖重宗之义也。吾丁氏之出罗州者。往往有显族。子之十三世以上。安知非蝉联盛阀。子之诸宗人之在越中者。长少计二百有馀人。其先祖积累之报。可验。大抵士大夫家显晦兴替。不在世序之远近。实系子孙贤不肖耳。诚使二百馀人者。家勉孝悌。户讲诗书。以振发其世业。则弗患其不为显人茂阀。而十三世以上祖考有灵。其不曰吾有后哉。其为尊祖重宗之义大矣。夫水出于山。而流派洪滥。则知其源之必大。木生于地。而柯叶
支。士大夫得以考识。故当楚汉扰攘之后。太史公叙次其先世。溯至唐虞之际。此三代所以劝民尊祖重宗之善教也。世级既降。此法遂废。无官籍而有家谱。壹经兵燹。荡佚其世次。则十数世以上。茫然不记其所出。与编户小民无异。而东国尤甚。诚可悲也。丁君载遇遣其弟载选。谂余曰。吾十三世祖某。自义城移家于宁越郡。遭寇难。佚世谱。十三世以上官爵名字。无所考。十三世以下。簪缨遂绝。门阀寝微。而此后世故不可知。大惧卒至泯晦。遂自十三世始。撰次其代序宗支生卒配耦。为一谱。谋宗人鸠财力。将付诸剞劂。传之子孙。为无穷计。执事其怜而惠一言为序。言已。貌若甚戚。余告之曰。善乎。此尊祖重宗之义也。吾丁氏之出罗州者。往往有显族。子之十三世以上。安知非蝉联盛阀。子之诸宗人之在越中者。长少计二百有馀人。其先祖积累之报。可验。大抵士大夫家显晦兴替。不在世序之远近。实系子孙贤不肖耳。诚使二百馀人者。家勉孝悌。户讲诗书。以振发其世业。则弗患其不为显人茂阀。而十三世以上祖考有灵。其不曰吾有后哉。其为尊祖重宗之义大矣。夫水出于山。而流派洪滥。则知其源之必大。木生于地。而柯叶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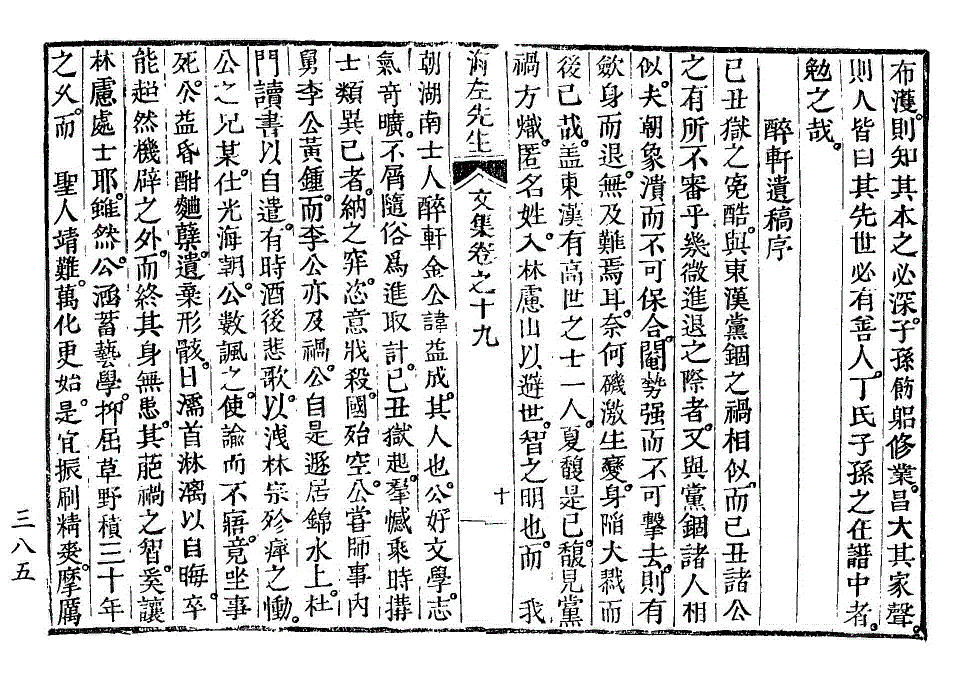 布濩。则知其本之必深。子孙饬躬修业。昌大其家声。则人皆曰其先世必有善人。丁氏子孙之在谱中者。勉之哉。
布濩。则知其本之必深。子孙饬躬修业。昌大其家声。则人皆曰其先世必有善人。丁氏子孙之在谱中者。勉之哉。醉轩遗稿序
己丑狱之冤酷。与东汉党锢之祸相似。而己丑诸公之有所不审乎几微进退之际者。又与党锢诸人相似。夫朝象溃而不可保合。阉势强而不可击去。则有敛身而退。无及难焉耳。奈何矶激生变。身陷大戮而后已哉。盖东汉有高世之士一人。夏馥是已。馥见党祸方炽。匿名姓。入林虑山以避世。智之明也。而 我朝湖南士人醉轩金公讳益成。其人也。公好文学。志气奇旷。不屑随俗为进取计。己丑狱起。群憾乘时搆士类异己者。纳之阱。恣意戕杀。国殆空。公尝师事内舅李公黄钟。而李公亦及祸。公自是遁居锦水上。杜门读书以自遣。有时酒后悲歌。以泄林宗殄瘁之恸。公之兄某。仕光海朝。公数讽之。使谕而不寤。竟坐事死。公益昏酣曲蘖。遗弃形骸。日濡首淋漓以自晦。卒能超然机辟之外。而终其身无患。其萉祸之智。奚让林虑处士耶。虽然。公涵蓄艺学。抑屈草野积三十年之久。而 圣人靖难。万化更始。是宜振刷精爽。摩厉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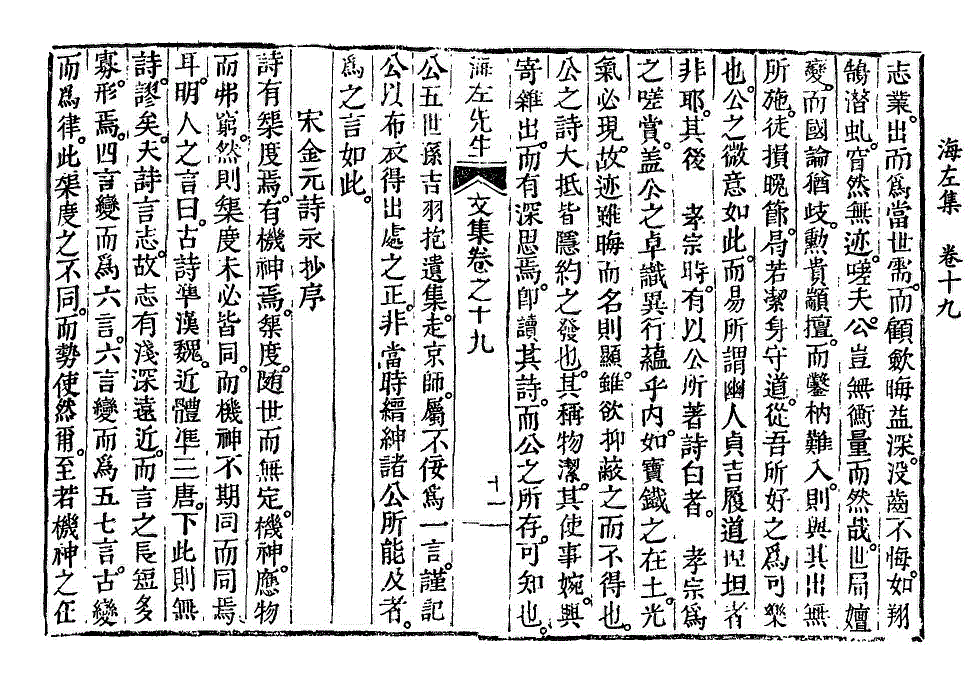 志业。出而为当世需。而顾敛晦益深。没齿不悔。如翔鹄潜虬。窅然无迹。嗟夫。公岂无衡量而然哉。世局嬗变。而国论犹歧。勋贵颛擅。而凿枘难入。则与其出无所施。徒损晚节。曷若洁身守道。从吾所好之为可乐也。公之微意如此。而易所谓幽人贞吉履道埋坦者非耶。其后 孝宗时。有以公所著诗白者。 孝宗为之嗟赏。盖公之卓识异行蕴乎内。如宝铁之在土。光气必现。故迹虽晦而名则显。虽欲抑蔽之而不得也。公之诗大抵皆隐约之发也。其称物洁。其使事婉。兴寄杂出。而有深思焉。即读其诗。而公之所存。可知也。公五世孙吉羽抱遗集。走京师。属不佞为一言。谨记公以布衣得出处之正。非当时缙绅诸公所能及者。为之言如此。
志业。出而为当世需。而顾敛晦益深。没齿不悔。如翔鹄潜虬。窅然无迹。嗟夫。公岂无衡量而然哉。世局嬗变。而国论犹歧。勋贵颛擅。而凿枘难入。则与其出无所施。徒损晚节。曷若洁身守道。从吾所好之为可乐也。公之微意如此。而易所谓幽人贞吉履道埋坦者非耶。其后 孝宗时。有以公所著诗白者。 孝宗为之嗟赏。盖公之卓识异行蕴乎内。如宝铁之在土。光气必现。故迹虽晦而名则显。虽欲抑蔽之而不得也。公之诗大抵皆隐约之发也。其称物洁。其使事婉。兴寄杂出。而有深思焉。即读其诗。而公之所存。可知也。公五世孙吉羽抱遗集。走京师。属不佞为一言。谨记公以布衣得出处之正。非当时缙绅诸公所能及者。为之言如此。宋金元诗永抄序
诗有矩度焉。有机神焉。矩度。随世而无定。机神。应物而弗穷。然则矩度末必皆同。而机神不期同而同焉耳。明人之言曰。古诗准汉魏。近体准三唐。下此则无诗。谬矣。夫诗言志。故志有浅深远近。而言之长短多寡。形焉。四言变而为六言。六言变而为五七言。古变而为律。此矩度之不同。而势使然尔。至若机神之在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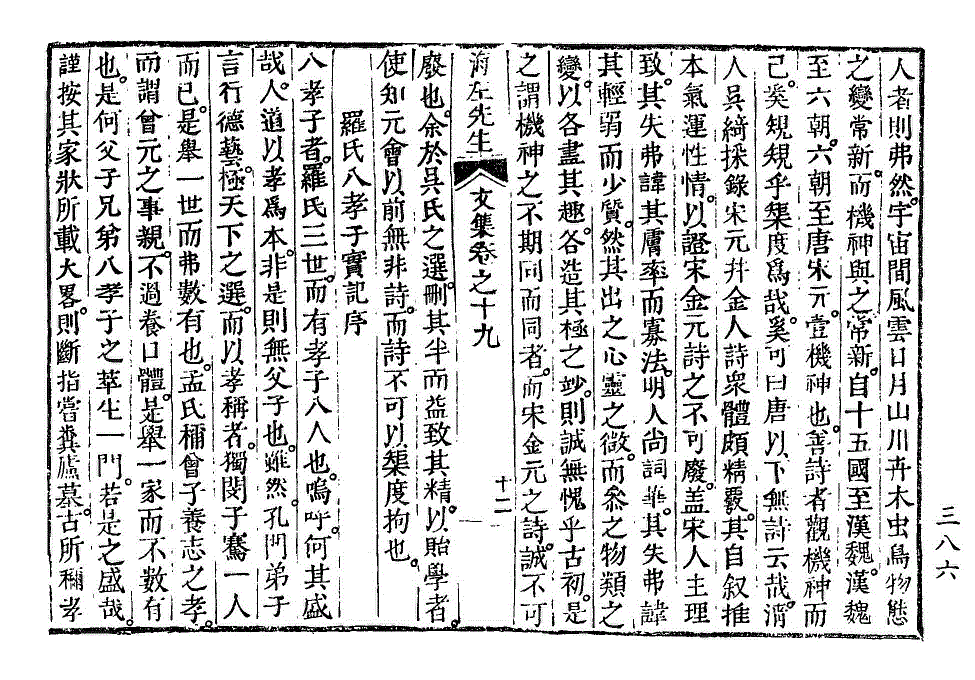 人者则弗然。宇宙间风云日月山川卉木虫鸟物态之变常新。而机神与之常新。自十五国至汉魏。汉魏至六朝。六朝至唐宋元。壹机神也。善诗者观机神而已。奚规规乎矩度为哉。奚可曰唐以下无诗云哉。清人吴绮采录宋元并金人诗众体颇精覈。其自叙推本气运性情。以證宋金元诗之不可废。盖宋人主理致。其失弗讳其肤率而寡法。明人尚词华。其失弗讳其轻弱而少质。然其出之心灵之微。而参之物类之变。以各尽其趣。各造其极之妙。则诚无愧乎古初。是之谓机神之不期同而同者。而宋金元之诗。诚不可废也。余于吴氏之选。删其半而益致其精。以贻学者。使知元会以前无非诗。而诗不可以矩度拘也。
人者则弗然。宇宙间风云日月山川卉木虫鸟物态之变常新。而机神与之常新。自十五国至汉魏。汉魏至六朝。六朝至唐宋元。壹机神也。善诗者观机神而已。奚规规乎矩度为哉。奚可曰唐以下无诗云哉。清人吴绮采录宋元并金人诗众体颇精覈。其自叙推本气运性情。以證宋金元诗之不可废。盖宋人主理致。其失弗讳其肤率而寡法。明人尚词华。其失弗讳其轻弱而少质。然其出之心灵之微。而参之物类之变。以各尽其趣。各造其极之妙。则诚无愧乎古初。是之谓机神之不期同而同者。而宋金元之诗。诚不可废也。余于吴氏之选。删其半而益致其精。以贻学者。使知元会以前无非诗。而诗不可以矩度拘也。罗氏八孝子实记序
八孝子者。罗氏三世。而有孝子八人也。呜呼。何其盛哉。人道以孝为本。非是则无父子也。虽然。孔门弟子言行德艺。极天下之选。而以孝称者。独闵子骞一人而已。是举一世而弗数有也。孟氏称曾子养志之孝。而谓曾元之事亲。不过养口体。是举一家而不数有也。是何父子兄弟八孝子之萃生一门。若是之盛哉。谨按其家状所载大略。则断指尝粪庐墓。古所称孝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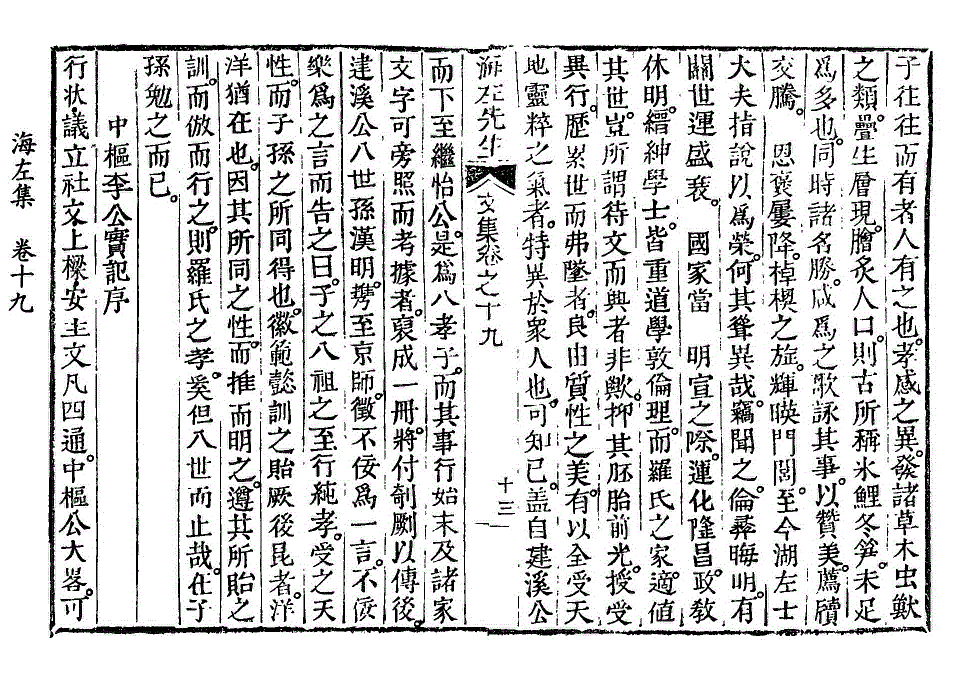 子往往而有者人有之也。孝感之异。发诸草木虫兽之类。叠生层现。脍炙人口。则古所称冰鲤冬笋。未足为多也。同时诸名胜。咸为之歌咏其事。以赞美。荐牍交腾。 恩褒屡降。棹楔之㫌。辉映门闾。至今湖左士大夫指说以为荣。何其耸异哉。窃闻之。伦彝晦明。有关世运盛衰。 国家当 明宣之际。运化隆昌。政教休明。缙绅学士。皆重道学敦伦理。而罗氏之家。适值其世。岂所谓待文而兴者非欤。抑其胚胎前光。授受异行。历累世而弗坠者。良由质性之美。有以全受天地灵粹之气者。特异于众人也。可知已。盖自建溪公而下至继怡公。是为八孝子。而其事行始末及诸家文字可旁照而考据者。裒成一册。将付剞劂以传后。建溪公八世孙汉明。携至京师。徵不佞为一言。不佞乐为之言而告之曰。子之八祖之至行纯孝。受之天性。而子孙之所同得也。徽范懿训之贻厥后昆者。洋洋犹在也。因其所同之性。而推而明之。遵其所贻之训。而傲而行之。则罗氏之孝。奚但八世而止哉。在子孙勉之而已。
子往往而有者人有之也。孝感之异。发诸草木虫兽之类。叠生层现。脍炙人口。则古所称冰鲤冬笋。未足为多也。同时诸名胜。咸为之歌咏其事。以赞美。荐牍交腾。 恩褒屡降。棹楔之㫌。辉映门闾。至今湖左士大夫指说以为荣。何其耸异哉。窃闻之。伦彝晦明。有关世运盛衰。 国家当 明宣之际。运化隆昌。政教休明。缙绅学士。皆重道学敦伦理。而罗氏之家。适值其世。岂所谓待文而兴者非欤。抑其胚胎前光。授受异行。历累世而弗坠者。良由质性之美。有以全受天地灵粹之气者。特异于众人也。可知已。盖自建溪公而下至继怡公。是为八孝子。而其事行始末及诸家文字可旁照而考据者。裒成一册。将付剞劂以传后。建溪公八世孙汉明。携至京师。徵不佞为一言。不佞乐为之言而告之曰。子之八祖之至行纯孝。受之天性。而子孙之所同得也。徽范懿训之贻厥后昆者。洋洋犹在也。因其所同之性。而推而明之。遵其所贻之训。而傲而行之。则罗氏之孝。奚但八世而止哉。在子孙勉之而已。中枢李公实记序
行状,议立社文,上梁,安主文凡四通。中枢公大略。可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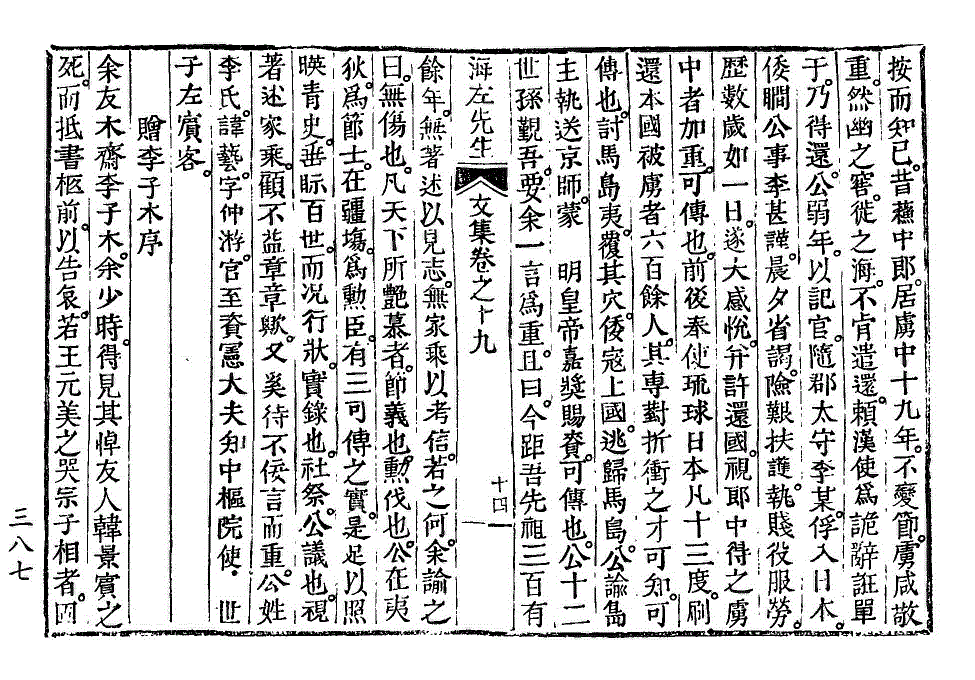 按而知已。昔苏中郎。居虏中十九年。不变节。虏咸敬重。然幽之窖。徙之海。不肯遣还。赖汉使为诡辞诳单于。乃得还。公弱年。以记官。随郡太守李某。俘入日本。倭瞷公事李甚谨。晨夕省谒。险艰扶护。执贱役服劳。历数岁如一日。遂大感悦。并许还国。视郎中得之虏中者加重。可传也。前后奉使琉球日本凡十三度。刷还本国被虏者六百馀人。其专对折冲之才可知。可传也。讨马岛夷。覆其穴。倭寇上国。逃归马岛。公谕岛主执送京师。蒙 明皇帝嘉奖赐赉。可传也。公十二世孙觐吾。要余一言为重。且曰。今距吾先祖三百有馀年。无著述以见志。无家乘以考信。若之何。余谕之曰。无伤也。凡天下所艳慕者。节义也。勋伐也。公在夷狄。为节士。在疆场。为勋臣。有三可传之实。是足以照映青史。垂视百世。而况行状。实录也。社祭。公议也。视著述家乘。顾不益章章欤。又奚待不佞言而重。公姓李氏。讳艺。字仲游。官至资宪大夫知中枢院使, 世子左宾客。
按而知已。昔苏中郎。居虏中十九年。不变节。虏咸敬重。然幽之窖。徙之海。不肯遣还。赖汉使为诡辞诳单于。乃得还。公弱年。以记官。随郡太守李某。俘入日本。倭瞷公事李甚谨。晨夕省谒。险艰扶护。执贱役服劳。历数岁如一日。遂大感悦。并许还国。视郎中得之虏中者加重。可传也。前后奉使琉球日本凡十三度。刷还本国被虏者六百馀人。其专对折冲之才可知。可传也。讨马岛夷。覆其穴。倭寇上国。逃归马岛。公谕岛主执送京师。蒙 明皇帝嘉奖赐赉。可传也。公十二世孙觐吾。要余一言为重。且曰。今距吾先祖三百有馀年。无著述以见志。无家乘以考信。若之何。余谕之曰。无伤也。凡天下所艳慕者。节义也。勋伐也。公在夷狄。为节士。在疆场。为勋臣。有三可传之实。是足以照映青史。垂视百世。而况行状。实录也。社祭。公议也。视著述家乘。顾不益章章欤。又奚待不佞言而重。公姓李氏。讳艺。字仲游。官至资宪大夫知中枢院使, 世子左宾客。赠李子木序
余友木斋李子木。余少时。得见其悼友人韩景宾之死。而抵书柩前。以告哀。若王元美之哭宗子相者。固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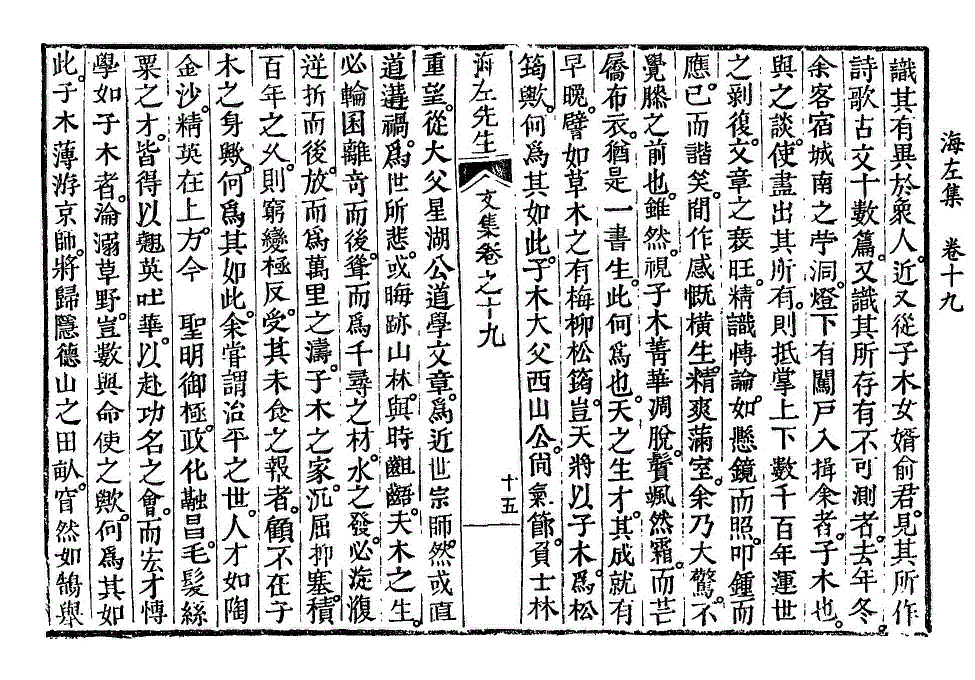 识其有异于众人。近又从子木女婿俞君。见其所作诗歌古文十数篇。又识其所存有不可测者。去年冬。余客宿城南之苧洞。灯下有闯户入揖余者。子木也。与之谈。使尽出其所有。则抵掌上下数千百年运世之剥复。文章之衰旺。精识博论。如悬镜而照。叩钟而应。已而谐笑。间作感慨横生。精爽满室。余乃大惊。不觉膝之前也。虽然。视子木菁华凋脱。鬓飒然霜。而芒屩布衣。犹是一书生。此何为也。天之生才。其成就有早晚。譬如草木之有梅柳松筠。岂天将以子木。为松筠欤。何为其如此。子木大父西山公。尚气节。负士林重望。从大父星湖公道学文章。为近世宗师。然或直道遘祸。为世所悲。或晦迹山林。与时龃龉。夫木之生。必轮囷离奇而后。耸而为千寻之材。水之发。必㳬澓逆折而后。放而为万里之涛。子木之家。沉屈抑塞。积百年之久。则穷变极反。受其未食之报者。顾不在子木之身欤。何为其如此。余尝谓治平之世。人才如陶金沙。精英在上。方今 圣明御极。政化融昌。毛发丝粟之才。皆得以翘英吐华。以赴功名之会。而宏才博学如子木者。沦溺草野。岂数与命使之欤。何为其如此。子木薄游京师。将归隐德山之田亩。窅然如鹄举
识其有异于众人。近又从子木女婿俞君。见其所作诗歌古文十数篇。又识其所存有不可测者。去年冬。余客宿城南之苧洞。灯下有闯户入揖余者。子木也。与之谈。使尽出其所有。则抵掌上下数千百年运世之剥复。文章之衰旺。精识博论。如悬镜而照。叩钟而应。已而谐笑。间作感慨横生。精爽满室。余乃大惊。不觉膝之前也。虽然。视子木菁华凋脱。鬓飒然霜。而芒屩布衣。犹是一书生。此何为也。天之生才。其成就有早晚。譬如草木之有梅柳松筠。岂天将以子木。为松筠欤。何为其如此。子木大父西山公。尚气节。负士林重望。从大父星湖公道学文章。为近世宗师。然或直道遘祸。为世所悲。或晦迹山林。与时龃龉。夫木之生。必轮囷离奇而后。耸而为千寻之材。水之发。必㳬澓逆折而后。放而为万里之涛。子木之家。沉屈抑塞。积百年之久。则穷变极反。受其未食之报者。顾不在子木之身欤。何为其如此。余尝谓治平之世。人才如陶金沙。精英在上。方今 圣明御极。政化融昌。毛发丝粟之才。皆得以翘英吐华。以赴功名之会。而宏才博学如子木者。沦溺草野。岂数与命使之欤。何为其如此。子木薄游京师。将归隐德山之田亩。窅然如鹄举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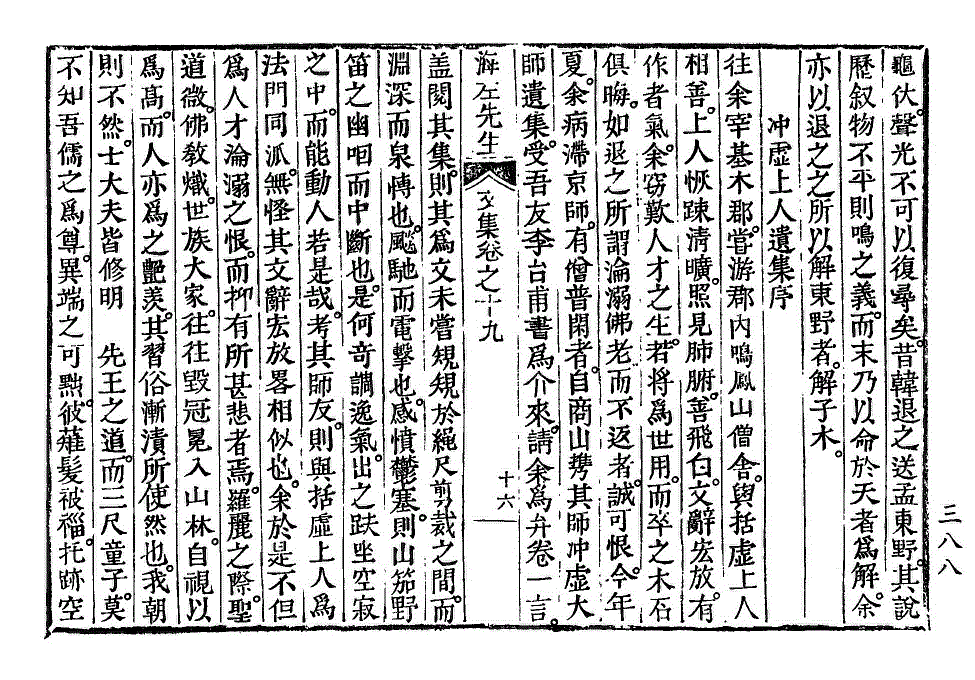 龟伏。声光不可以复寻矣。昔韩退之送孟东野。其说历叙物不平则鸣之义。而末乃以命于天者为解。余亦以退之之所以解东野者。解子木。
龟伏。声光不可以复寻矣。昔韩退之送孟东野。其说历叙物不平则鸣之义。而末乃以命于天者为解。余亦以退之之所以解东野者。解子木。冲虚上人遗集序
往余宰基木郡。尝游郡内鸣凤山僧舍。与括虚上人相善。上人恢疏清旷。照见肺腑。善飞白。文辞宏放。有作者气。余窃叹人才之生。若将为世用。而卒之木石俱晦。如退之所谓沦溺佛老而不返者。诚可恨。今年夏。余病滞京师。有僧普闲者。自商山携其师冲虚大师遗集。受吾友李台甫书为介来。请余为弁卷一言。盖阅其集。则其为文未尝规规于绳尺剪裁之间。而渊深而泉博也。飙驰而电击也。感愤郁塞。则山笳野笛之幽咽而中断也。是何奇调逸气。出之趺坐空寂之中。而能动人若是哉。考其师友。则与括虚上人为法门同派。无怪其文辞宏放略相似也。余于是不但为人才沦溺之恨。而抑有所甚悲者焉。罗丽之际。圣道微。佛教炽。世族大家。往往毁冠冕入山林。自视以为高。而人亦为之艳羡。其习俗渐渍所使然也。我朝则不然。士大夫皆修明 先王之道。而三尺童子。莫不知吾儒之为尊。异端之可黜。彼薙发被𥚉。托迹空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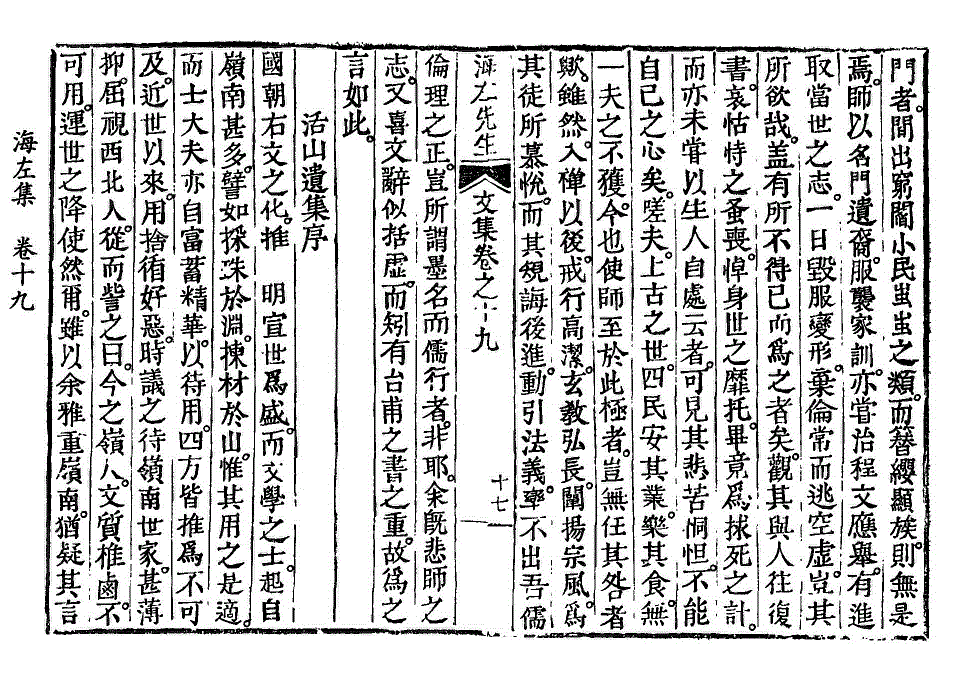 门者。间出穷阎小民蚩蚩之类。而簪缨显族。则无是焉。师以名门遗裔。服袭家训。亦尝治程文应举。有进取当世之志。一日毁服变形。弃伦常而逃空虚。岂其所欲哉。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者矣。观其与人往复书。哀怙恃之蚤丧。悼身世之靡托。毕竟为救死之计。而亦未尝以生人自处云者。可见其悲苦恫怛。不能自已之心矣。嗟夫。上古之世。四民安其业。乐其食。无一夫之不获。今也使师至于此极者。岂无任其咎者欤。虽然。入禅以后。戒行高洁。玄教弘长。阐扬宗风。为其徒所慕悦。而其规诲后进。动引法义。率不出吾儒伦理之正。岂所谓墨名而儒行者。非耶。余既悲师之志。又喜文辞似括虚。而矧有台甫之书之重。故为之言如此。
门者。间出穷阎小民蚩蚩之类。而簪缨显族。则无是焉。师以名门遗裔。服袭家训。亦尝治程文应举。有进取当世之志。一日毁服变形。弃伦常而逃空虚。岂其所欲哉。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者矣。观其与人往复书。哀怙恃之蚤丧。悼身世之靡托。毕竟为救死之计。而亦未尝以生人自处云者。可见其悲苦恫怛。不能自已之心矣。嗟夫。上古之世。四民安其业。乐其食。无一夫之不获。今也使师至于此极者。岂无任其咎者欤。虽然。入禅以后。戒行高洁。玄教弘长。阐扬宗风。为其徒所慕悦。而其规诲后进。动引法义。率不出吾儒伦理之正。岂所谓墨名而儒行者。非耶。余既悲师之志。又喜文辞似括虚。而矧有台甫之书之重。故为之言如此。活山遗集序
国朝右文之化。推 明宣世为盛。而文学之士。起自岭南甚多。譬如采珠于渊。拣材于山。惟其用之是适。而士大夫亦自富蓄精华。以待用。四方皆推为不可及。近世以来。用舍循好恶。时议之待岭南世家。甚薄抑。屈视西北人。从而訾之曰。今之岭人。文质椎卤。不可用。运世之降使然尔。虽以余雅重岭南。犹疑其言
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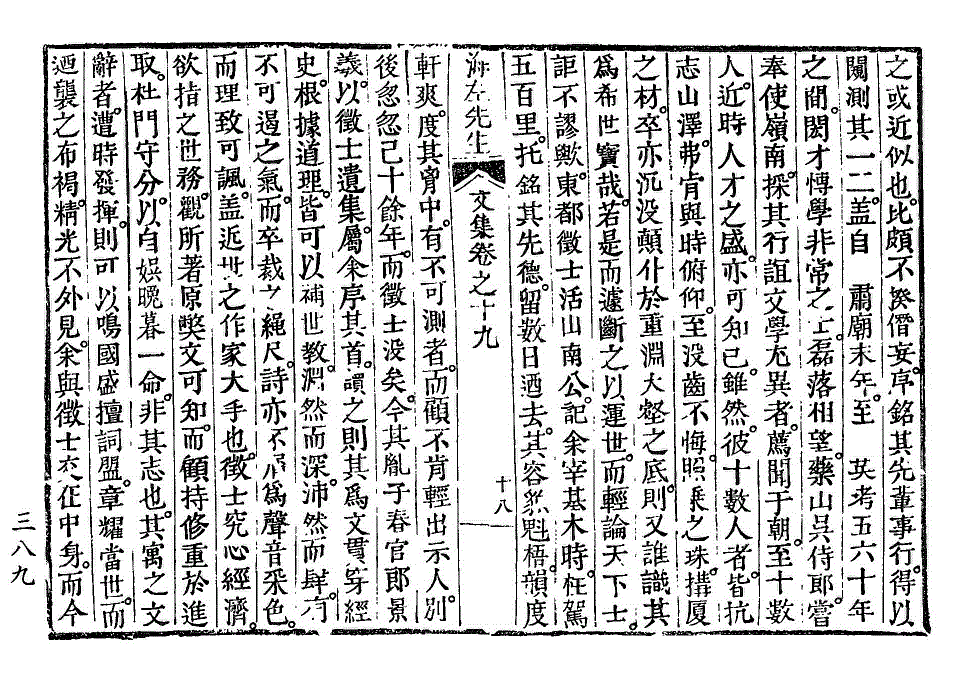 之或近似也。比颇不揆僭妄。序铭其先辈事行。得以窥测其一二。盖自 肃庙末年。至 英考五六十年之间。闳才博学非常之士。磊落相望。药山吴侍郎。尝奉使岭南。采其行谊文学尤异者。荐闻于朝。至十数人。近时人才之盛。亦可知已。虽然。彼十数人者。皆抗志山泽。弗肯与时俯仰。至没齿不悔。照乘之珠。搆厦之材。卒亦沉没颠仆于重渊大壑之底。则又谁识其为希世宝哉。若是而遽断之以运世。而轻论天下士。讵不谬欤。东都徵士活山南公。记余宰基木时。枉驾五百里。托铭其先德。留数日乃去。其容貌魁梧。韵度轩爽。度其胸中。有不可测者。而顾不肯轻出示人。别后忽忽已十馀年。而徵士没矣。今其胤子春官郎景羲。以徵士遗集。属余序其首。读之则其为文贯穿经史。根据道理。皆可以补世教。渊然而深。沛然而肆。有不可遏之气。而卒裁之绳尺。诗亦不屑为声音采色。而理致可讽。盖近世之作家大手也。徵士究心经济。欲指之世务。观所著原弊文可知。而顾持修重于进取。杜门守分。以自娱晚暮一命。非其志也。其寓之文辞者。遭时发挥。则可以鸣国盛擅词盟。章耀当世。而乃袭之布褐。精光不外见。余与徵士交在中身。而今
之或近似也。比颇不揆僭妄。序铭其先辈事行。得以窥测其一二。盖自 肃庙末年。至 英考五六十年之间。闳才博学非常之士。磊落相望。药山吴侍郎。尝奉使岭南。采其行谊文学尤异者。荐闻于朝。至十数人。近时人才之盛。亦可知已。虽然。彼十数人者。皆抗志山泽。弗肯与时俯仰。至没齿不悔。照乘之珠。搆厦之材。卒亦沉没颠仆于重渊大壑之底。则又谁识其为希世宝哉。若是而遽断之以运世。而轻论天下士。讵不谬欤。东都徵士活山南公。记余宰基木时。枉驾五百里。托铭其先德。留数日乃去。其容貌魁梧。韵度轩爽。度其胸中。有不可测者。而顾不肯轻出示人。别后忽忽已十馀年。而徵士没矣。今其胤子春官郎景羲。以徵士遗集。属余序其首。读之则其为文贯穿经史。根据道理。皆可以补世教。渊然而深。沛然而肆。有不可遏之气。而卒裁之绳尺。诗亦不屑为声音采色。而理致可讽。盖近世之作家大手也。徵士究心经济。欲指之世务。观所著原弊文可知。而顾持修重于进取。杜门守分。以自娱晚暮一命。非其志也。其寓之文辞者。遭时发挥。则可以鸣国盛擅词盟。章耀当世。而乃袭之布褐。精光不外见。余与徵士交在中身。而今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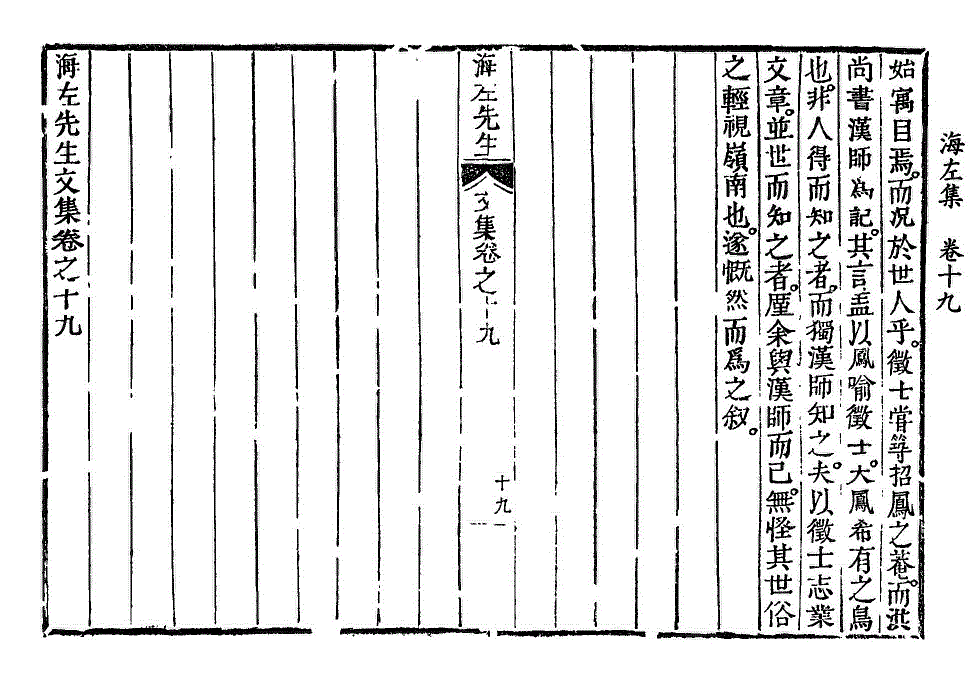 始寓目焉。而况于世人乎。徵士尝筑招凤之庵。而洪尚书汉师为记。其言盖以凤喻徵士。大凤希有之鸟也。非人得而知之者。而独汉师知之。夫以徵士志业文章。并世而知之者。廑余与汉师而已。无怪其世俗之轻视岭南也。遂慨然而为之叙。
始寓目焉。而况于世人乎。徵士尝筑招凤之庵。而洪尚书汉师为记。其言盖以凤喻徵士。大凤希有之鸟也。非人得而知之者。而独汉师知之。夫以徵士志业文章。并世而知之者。廑余与汉师而已。无怪其世俗之轻视岭南也。遂慨然而为之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