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本庵集卷四 第 x 页
本庵集卷四
书
书
本庵集卷四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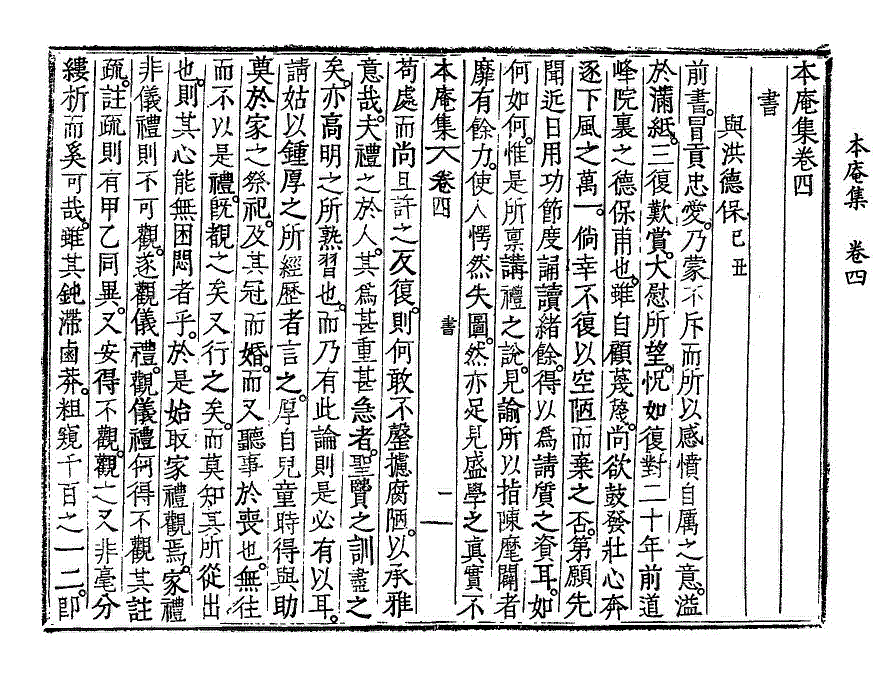 与洪德保(己丑)
与洪德保(己丑)前书。冒贡忠爱。乃蒙不斥而所以感愤自厉之意。溢于满纸。三复叹赏。大慰所望。恍如复对二十年前道峰院里之德保甫也。虽自顾蔑蔑。尚欲鼓发壮心奔逐下风之万一。倘幸不复以空陋而弃之否。第愿先闻近日用功节度诵读绪馀。得以为请质之资耳。如何如何。惟是所禀讲礼之说。见谕所以指陈麾辟者靡有馀力。使人愕然失图。然亦足见盛学之真实不苟处而尚且许之反复。则何敢不罄摅腐陋。以承雅意哉。夫礼之于人。其为甚重甚急者。圣贤之训尽之矣。亦高明之所熟习也。而乃有此论则是必有以耳。请姑以钟厚之所经历者言之。厚自儿童时得与助奠于家之祭祀。及其冠而婚。而又听事于丧也。无往而不以是礼。既睹之矣又行之矣。而莫知其所从出也。则其心能无困闷者乎。于是始取家礼观焉。家礼非仪礼则不可观。遂观仪礼。观仪礼何得不观其注疏。注疏则有甲乙同异。又安得不观。观之又非毫分缕析而奚可哉。虽其钝滞卤莽。粗窥千百之一二。即
本庵集卷四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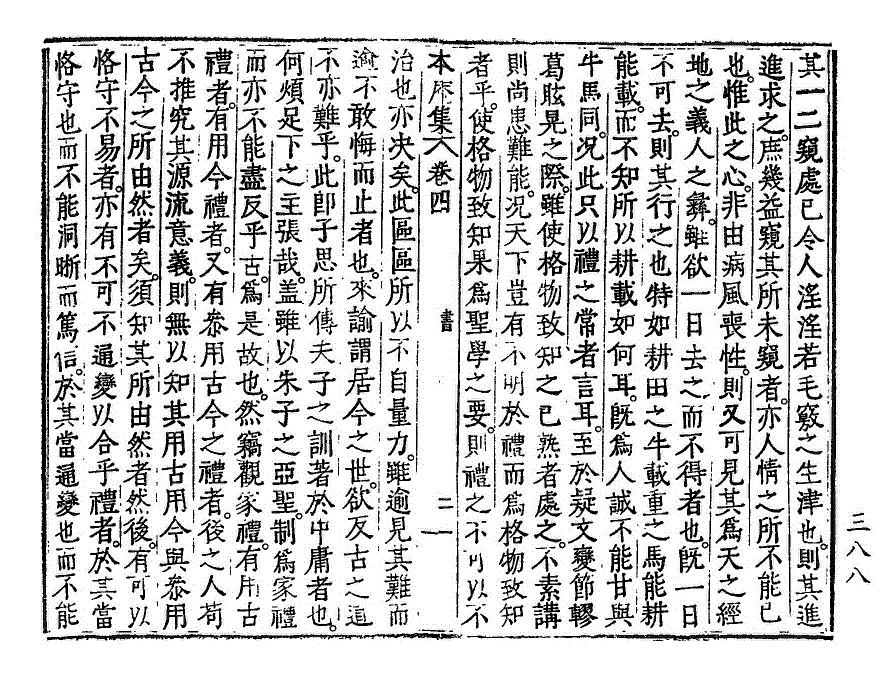 其一二窥处已令人淫淫若毛窍之生津也。则其进进求之。庶几益窥其所未窥者。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惟此之心。非由病风丧性。则又可见其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彝。虽欲一日去之而不得者也。既一日不可去。则其行之也特如耕田之牛载重之马能耕能载。而不知所以耕载如何耳。既为人诚不能甘与牛马同。况此只以礼之常者言耳。至于疑文变节轇葛眩晃之际。虽使格物致知之已熟者处之。不素讲则尚患难能。况天下岂有不明于礼而为格物致知者乎。使格物致知果为圣学之要。则礼之不可以不治也亦决矣。此区区所以不自量力。虽逾见其难而逾不敢悔而止者也。来谕谓居今之世。欲反古之道不亦难乎。此即子思所传夫子之训著于中庸者也。何烦足下之主张哉。盖虽以朱子之亚圣。制为家礼而亦不能尽反乎古。为是故也。然窃观家礼。有用古礼者。有用今礼者。又有参用古今之礼者。后之人苟不推究其源流意义。则无以知其用古用今与参用古今之所由然者矣。须知其所由然者然后。有可以恪守不易者。亦有不可不通变以合乎礼者。于其当恪守也而不能洞晰而笃信。于其当通变也而不能
其一二窥处已令人淫淫若毛窍之生津也。则其进进求之。庶几益窥其所未窥者。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惟此之心。非由病风丧性。则又可见其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彝。虽欲一日去之而不得者也。既一日不可去。则其行之也特如耕田之牛载重之马能耕能载。而不知所以耕载如何耳。既为人诚不能甘与牛马同。况此只以礼之常者言耳。至于疑文变节轇葛眩晃之际。虽使格物致知之已熟者处之。不素讲则尚患难能。况天下岂有不明于礼而为格物致知者乎。使格物致知果为圣学之要。则礼之不可以不治也亦决矣。此区区所以不自量力。虽逾见其难而逾不敢悔而止者也。来谕谓居今之世。欲反古之道不亦难乎。此即子思所传夫子之训著于中庸者也。何烦足下之主张哉。盖虽以朱子之亚圣。制为家礼而亦不能尽反乎古。为是故也。然窃观家礼。有用古礼者。有用今礼者。又有参用古今之礼者。后之人苟不推究其源流意义。则无以知其用古用今与参用古今之所由然者矣。须知其所由然者然后。有可以恪守不易者。亦有不可不通变以合乎礼者。于其当恪守也而不能洞晰而笃信。于其当通变也而不能本庵集卷四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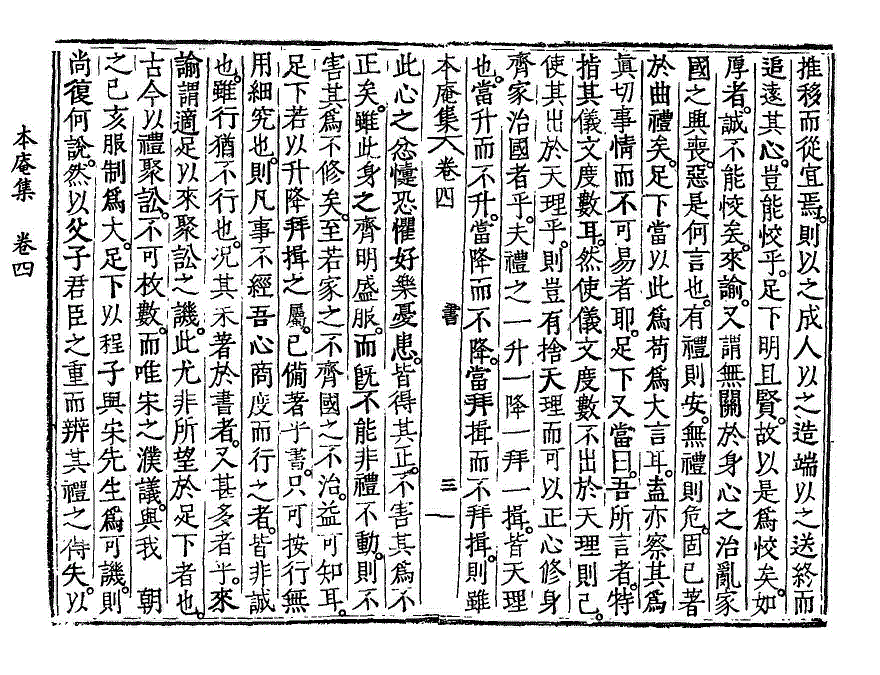 推移而从宜焉。则以之成人以之造端以之送终而追远其心。岂能恔乎。足下明且贤。故以是为恔矣。如厚者。诚不能恔矣。来谕。又谓无关于身心之治乱家国之兴丧。恶是何言也。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固已著于曲礼矣。足下当以此为苟为大言耳。盍亦察其为真切事情而不可易者耶。足下又当曰。吾所言者。特指其仪文度数耳。然使仪文度数不出于天理则已。使其出于天理乎。则岂有舍天理而可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者乎。夫礼之一升一降一拜一揖。皆天理也。当升而不升。当降而不降。当拜揖而不拜揖。则虽此心之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不害其为不正矣。虽此身之齐明盛服。而既不能非礼不动。则不害其为不修矣。至若家之不齐国之不治。益可知耳。足下若以升降拜揖之属。已备著乎书。只可按行无用细究也。则凡事不经吾心商度而行之者。皆非诚也。虽行犹不行也。况其未著于书者。又甚多者乎。来谕谓适足以来聚讼之讥。此尤非所望于足下者也。古今以礼聚讼。不可枚数。而唯宋之濮议。与我 朝之己亥服制为大。足下以程子与宋先生为可讥。则尚复何说。然以父子君臣之重而辨其礼之得失。以
推移而从宜焉。则以之成人以之造端以之送终而追远其心。岂能恔乎。足下明且贤。故以是为恔矣。如厚者。诚不能恔矣。来谕。又谓无关于身心之治乱家国之兴丧。恶是何言也。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固已著于曲礼矣。足下当以此为苟为大言耳。盍亦察其为真切事情而不可易者耶。足下又当曰。吾所言者。特指其仪文度数耳。然使仪文度数不出于天理则已。使其出于天理乎。则岂有舍天理而可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者乎。夫礼之一升一降一拜一揖。皆天理也。当升而不升。当降而不降。当拜揖而不拜揖。则虽此心之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不害其为不正矣。虽此身之齐明盛服。而既不能非礼不动。则不害其为不修矣。至若家之不齐国之不治。益可知耳。足下若以升降拜揖之属。已备著乎书。只可按行无用细究也。则凡事不经吾心商度而行之者。皆非诚也。虽行犹不行也。况其未著于书者。又甚多者乎。来谕谓适足以来聚讼之讥。此尤非所望于足下者也。古今以礼聚讼。不可枚数。而唯宋之濮议。与我 朝之己亥服制为大。足下以程子与宋先生为可讥。则尚复何说。然以父子君臣之重而辨其礼之得失。以本庵集卷四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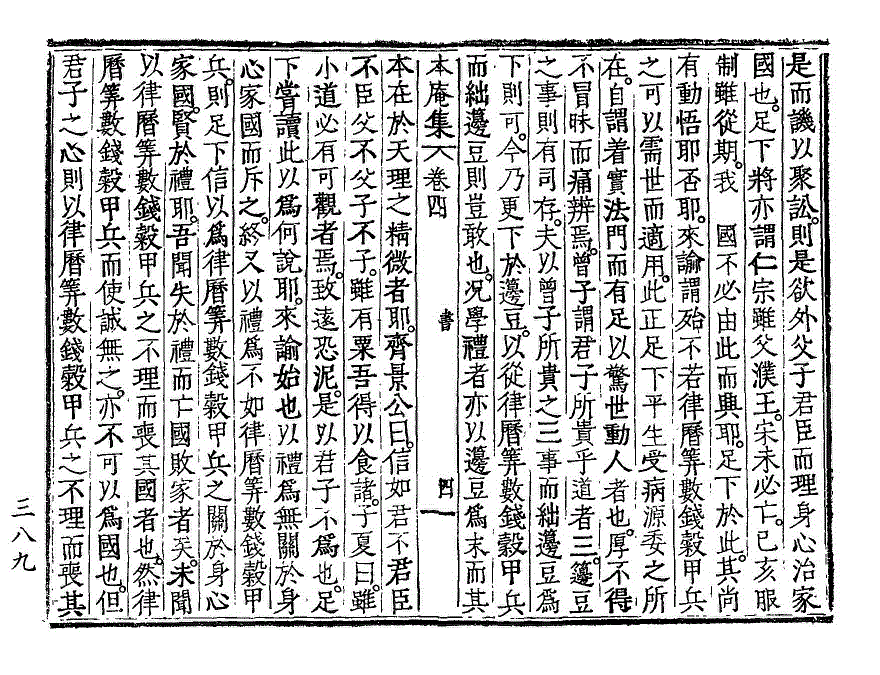 是而讥以聚讼。则是欲外父子君臣而理身心治家国也。足下将亦谓仁宗虽父濮王。宋未必亡。己亥服制虽从期。我 国不必由此而兴耶。足下于此。其尚有动悟耶否耶。来谕谓殆不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可以需世而适用。此正足下平生受病源委之所在。自谓着实法门而有足以惊世动人者也。厚不得不冒昧而痛辨焉。曾子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夫以曾子所贵之三事而绌笾豆为下则可。今乃更下于笾豆。以从律历算数钱谷甲兵而绌笾豆则岂敢也。况学礼者亦以笾豆为末而其本在于天理之精微者耶。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以食诸。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足下尝读此以为何说耶。来谕始也以礼为无关于身心家国而斥之。终又以礼为不如律历算数钱谷甲兵。则足下信以为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关于身心家国。贤于礼耶。吾闻失于礼而亡国败家者矣。未闻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不理而丧其国者也。然律历算数钱谷甲兵而使诚无之。亦不可以为国也。但君子之心则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不理而丧其
是而讥以聚讼。则是欲外父子君臣而理身心治家国也。足下将亦谓仁宗虽父濮王。宋未必亡。己亥服制虽从期。我 国不必由此而兴耶。足下于此。其尚有动悟耶否耶。来谕谓殆不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可以需世而适用。此正足下平生受病源委之所在。自谓着实法门而有足以惊世动人者也。厚不得不冒昧而痛辨焉。曾子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夫以曾子所贵之三事而绌笾豆为下则可。今乃更下于笾豆。以从律历算数钱谷甲兵而绌笾豆则岂敢也。况学礼者亦以笾豆为末而其本在于天理之精微者耶。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以食诸。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足下尝读此以为何说耶。来谕始也以礼为无关于身心家国而斥之。终又以礼为不如律历算数钱谷甲兵。则足下信以为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关于身心家国。贤于礼耶。吾闻失于礼而亡国败家者矣。未闻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不理而丧其国者也。然律历算数钱谷甲兵而使诚无之。亦不可以为国也。但君子之心则以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之不理而丧其本庵集卷四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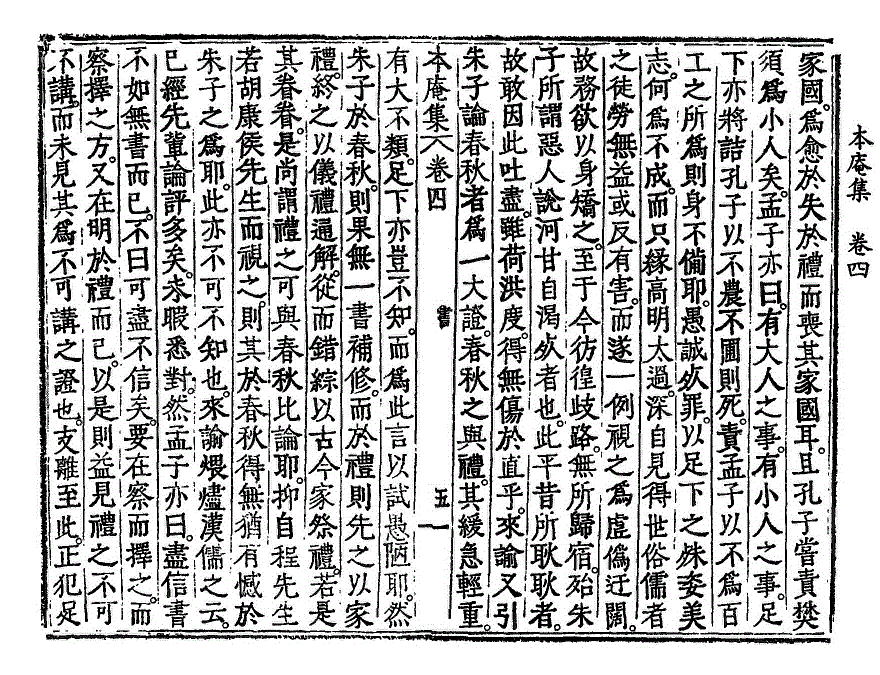 家国。为愈于失于礼而丧其家国耳。且孔子尝责樊须为小人矣。孟子亦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足下亦将诘孔子以不农不圃则死。责孟子以不为百工之所为则身不备耶。愚诚死罪。以足下之殊姿美志。何为不成。而只缘高明太过。深自见得世俗儒者之徒劳无益或反有害。而遂一例视之为虚伪迂阔。故务欲以身矫之。至于今彷徨歧路。无所归宿。殆朱子所谓恶人说河甘自渴死者也。此平昔所耿耿者。故敢因此吐尽。虽荷洪度。得无伤于直乎。来谕又引朱子论春秋者为一大證。春秋之与礼。其缓急轻重。有大不类。足下亦岂不知。而为此言以试愚陋耶。然朱子于春秋。则果无一书补修。而于礼则先之以家礼。终之以仪礼通解。从而错综以古今家祭礼。若是其眷眷。是尚谓礼之可与春秋比论耶。抑自程先生若胡康侯先生而视之。则其于春秋得无犹有憾于朱子之为耶。此亦不可不知也。来谕煨烬汉儒之云。已经先辈论评多矣。未暇悉对。然孟子亦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已。不曰可尽不信矣。要在察而择之。而察择之方。又在明于礼而已。以是则益见礼之不可不讲。而未见其为不可讲之證也。支离至此。正犯足
家国。为愈于失于礼而丧其家国耳。且孔子尝责樊须为小人矣。孟子亦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足下亦将诘孔子以不农不圃则死。责孟子以不为百工之所为则身不备耶。愚诚死罪。以足下之殊姿美志。何为不成。而只缘高明太过。深自见得世俗儒者之徒劳无益或反有害。而遂一例视之为虚伪迂阔。故务欲以身矫之。至于今彷徨歧路。无所归宿。殆朱子所谓恶人说河甘自渴死者也。此平昔所耿耿者。故敢因此吐尽。虽荷洪度。得无伤于直乎。来谕又引朱子论春秋者为一大證。春秋之与礼。其缓急轻重。有大不类。足下亦岂不知。而为此言以试愚陋耶。然朱子于春秋。则果无一书补修。而于礼则先之以家礼。终之以仪礼通解。从而错综以古今家祭礼。若是其眷眷。是尚谓礼之可与春秋比论耶。抑自程先生若胡康侯先生而视之。则其于春秋得无犹有憾于朱子之为耶。此亦不可不知也。来谕煨烬汉儒之云。已经先辈论评多矣。未暇悉对。然孟子亦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已。不曰可尽不信矣。要在察而择之。而察择之方。又在明于礼而已。以是则益见礼之不可不讲。而未见其为不可讲之證也。支离至此。正犯足本庵集卷四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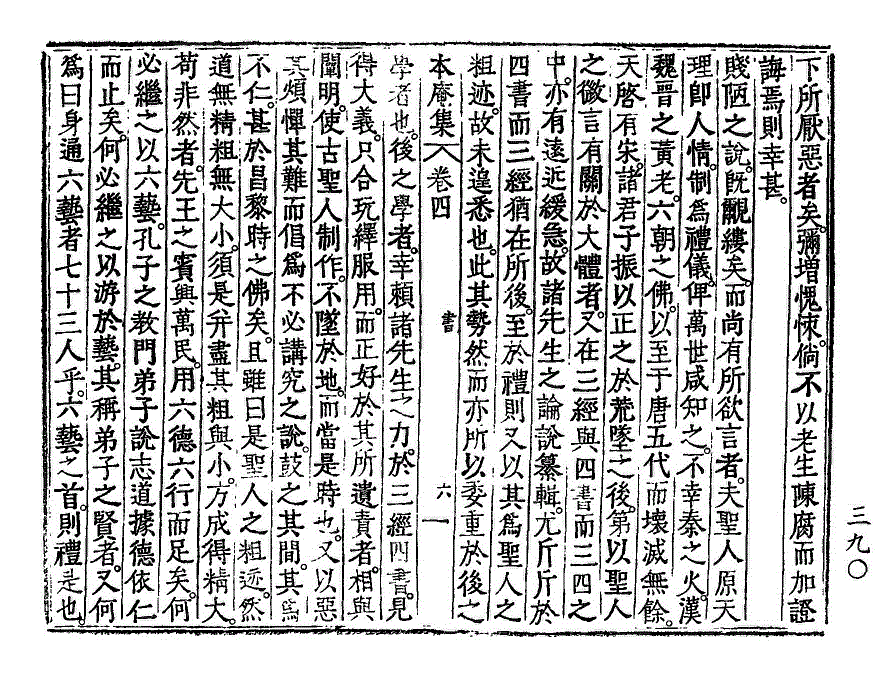 下所厌恶者矣。弥增愧悚。倘不以老生陈腐而加證诲焉则幸甚。
下所厌恶者矣。弥增愧悚。倘不以老生陈腐而加證诲焉则幸甚。贱陋之说。既覼缕矣。而尚有所欲言者。夫圣人原天理即人情。制为礼仪。俾万世咸知之。不幸秦之火。汉魏晋之黄老。六朝之佛。以至于唐五代而坏灭无馀。天启有宋。诸君子振以正之于荒坠之后。第以圣人之微言有关于大体者。又在三经与四书而三四之中。亦有远近缓急。故诸先生之论说纂辑。尤斤斤于四书而三经犹在所后。至于礼则又以其为圣人之粗迹。故未遑悉也。此其势然而亦所以委重于后之学者也。后之学者。幸赖诸先生之力。于三经四书。见得大义。只合玩绎服用。而正好于其所遗责者。相与阐明。使古圣人制作。不坠于地。而当是时也。又以恶其烦惮其难而倡为不必讲究之说。鼓之其间。其为不仁。甚于昌黎时之佛矣。且虽曰是圣人之粗迹。然道无精粗无大小。须是并尽其粗与小。方成得精大。苟非然者。先王之宾兴万民。用六德六行而足矣。何必继之以六艺。孔子之教门弟子说志道据德依仁而止矣。何必继之以游于艺。其称弟子之贤者。又何为曰身通六艺者七十三人乎。六艺之首。则礼是也。
本庵集卷四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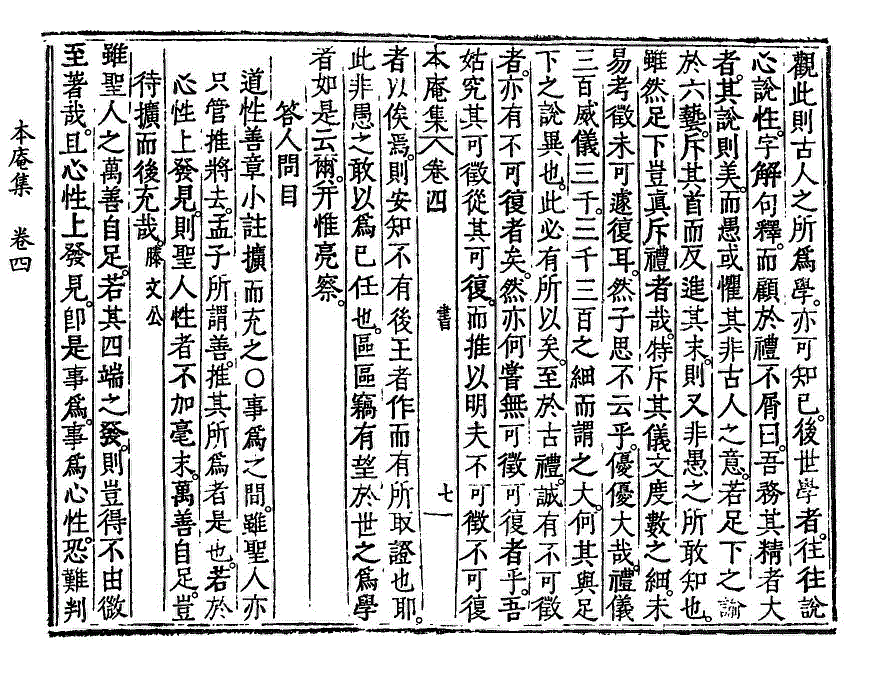 观此则古人之所为学。亦可知已。后世学者。往往说心说性。字解句释。而顾于礼不屑曰。吾务其精者大者。其说则美。而愚或惧其非古人之意。若足下之谕于六艺。斥其首而反进其末。则又非愚之所敢知也。虽然足下岂真斥礼者哉。特斥其仪文度数之细。未易考徵未可遽复耳。然子思不云乎。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三千三百之细而谓之大。何其与足下之说异也。此必有所以矣。至于古礼。诚有不可徵者。亦有不可复者矣。然亦何尝无可徵可复者乎。吾姑究其可徵从其可复。而推以明夫不可徵不可复者以俟焉。则安知不有后王者作而有所取證也耶。此非愚之敢以为己任也。区区窃有望于世之为学者如是云尔。并惟亮察。
观此则古人之所为学。亦可知已。后世学者。往往说心说性。字解句释。而顾于礼不屑曰。吾务其精者大者。其说则美。而愚或惧其非古人之意。若足下之谕于六艺。斥其首而反进其末。则又非愚之所敢知也。虽然足下岂真斥礼者哉。特斥其仪文度数之细。未易考徵未可遽复耳。然子思不云乎。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三千三百之细而谓之大。何其与足下之说异也。此必有所以矣。至于古礼。诚有不可徵者。亦有不可复者矣。然亦何尝无可徵可复者乎。吾姑究其可徵从其可复。而推以明夫不可徵不可复者以俟焉。则安知不有后王者作而有所取證也耶。此非愚之敢以为己任也。区区窃有望于世之为学者如是云尔。并惟亮察。答人问目
道性善章小注扩而充之○事为之间。虽圣人亦只管推将去。孟子所谓善。推其所为者是也。若于心性上发见。则圣人性者不加毫末。万善自足。岂待扩而后充哉。(滕文公)
虽圣人之万善自足。若其四端之发。则岂得不由微至著哉。且心性上发见。即是事为。事为心性。恐难判
本庵集卷四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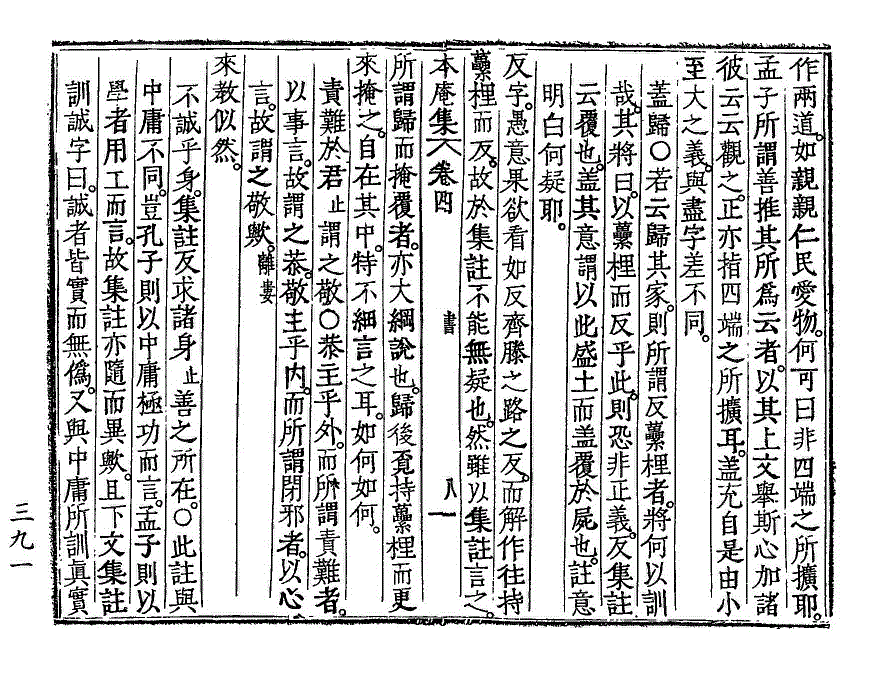 作两道。如亲亲仁民爱物。何可曰非四端之所扩耶。孟子所谓善推其所为云者。以其上文举斯心加诸彼云云观之。正亦指四端之所扩耳。盖充自是由小至大之义。与尽字差不同。
作两道。如亲亲仁民爱物。何可曰非四端之所扩耶。孟子所谓善推其所为云者。以其上文举斯心加诸彼云云观之。正亦指四端之所扩耳。盖充自是由小至大之义。与尽字差不同。盖归○若云归其家。则所谓反蔂梩者。将何以训哉。其将曰。以蔂梩而反乎此。则恐非正义。反集注云覆也。盖其意谓以此盛土而盖覆于尸也。注意明白何疑耶。
反字。愚意果欲看如反齐滕之路之反。而解作往持蔂梩而反。故于集注不能无疑也。然虽以集注言之。所谓归而掩覆者。亦大纲说也。归后觅持蔂梩而更来掩之。自在其中。特不细言之耳。如何如何。
责难于君(止)谓之敬○恭主乎外。而所谓责难者。以事言。故谓之恭。敬主乎内。而所谓闭邪者。以心言。故谓之敬欤。(离娄)
来教似然。
不诚乎身。集注反求诸身(止)善之所在。○此注与中庸不同。岂孔子则以中庸极功而言。孟子则以学者用工而言。故集注亦随而异欤。且下文集注训诚字曰。诚者皆实而无伪。又与中庸所训真实
本庵集卷四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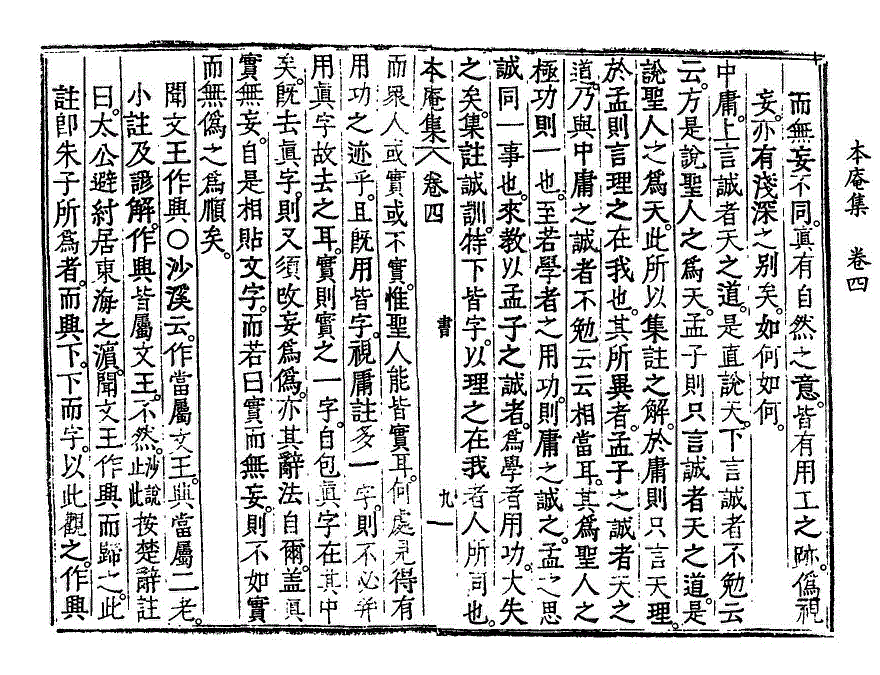 而无妄不同。真有自然之意。皆有用工之迹。伪视妄。亦有浅深之别矣。如何如何。
而无妄不同。真有自然之意。皆有用工之迹。伪视妄。亦有浅深之别矣。如何如何。中庸。上言诚者天之道。是直说天。下言诚者不勉云云。方是说圣人之为天。孟子则只言诚者天之道。是说圣人之为天。此所以集注之解。于庸则只言天理。于孟则言理之在我也。其所异者。孟子之诚者天之道。乃与中庸之诚者不勉云云相当耳。其为圣人之极功则一也。至若学者之用功。则庸之诚之。孟之思诚同一事也。来教以孟子之诚者。为学者用功。大失之矣。集注诚训。特下皆字。以理之在我者人所司也。而众人或实或不实。惟圣人能皆实耳。何处见得有用功之迹乎。且既用皆字。视庸注多一字。则不必并用真字故去之耳。实则实之一字。自包真字在其中矣。既去真字。则又须改妄为伪。亦其辞法自尔。盖真实无妄。自是相贴文字。而若曰实而无妄。则不如实而无伪之为顺矣。
闻文王作兴○沙溪云。作当属文王。兴当属二老。小注及谚解。作兴皆属文王。不然。(沙说止此。)按楚辞注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而归之。此注即朱子所为者。而兴下。下而字。以此观之。作兴
本庵集卷四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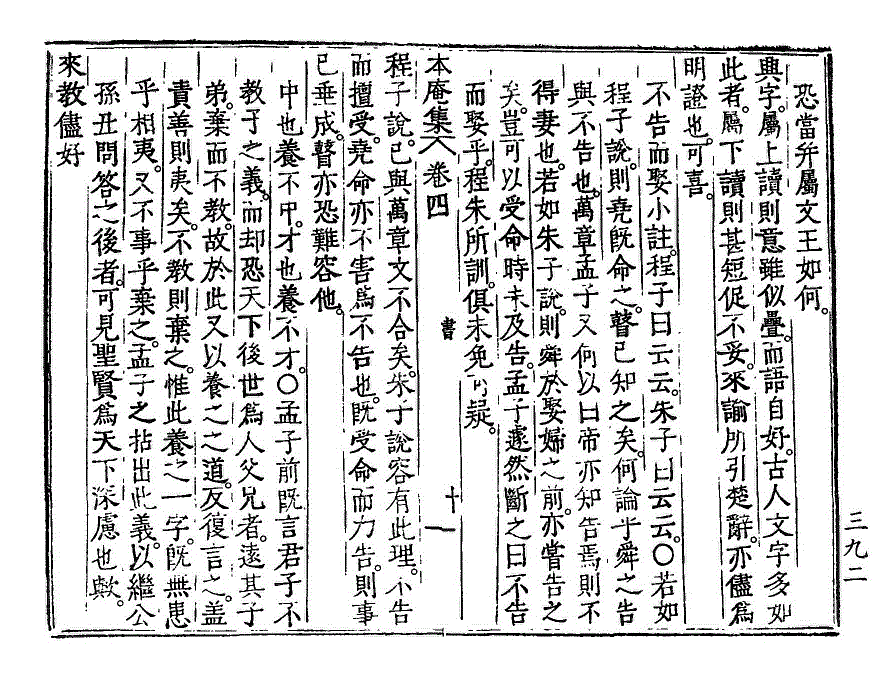 恐当并属文王如何。
恐当并属文王如何。兴字。属上读则意虽似叠。而语自好。古人文字多如此者。属下读则甚短促不妥。来谕所引楚辞。亦尽为明證也。可喜。
不告而娶小注。程子曰云云。朱子曰云云。○若如程子说。则尧既命之。瞽已知之矣。何论乎舜之告与不告也。万章孟子又何以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若如朱子说。则舜于娶妇之前。亦尝告之矣。岂可以受命时未及告。孟子遽然断之曰不告而娶乎。程朱所训。俱未免可疑。
程子说。已与万章文不合矣。朱子说容有此理。不告而擅受。尧命亦不害为不告也。既受命而力告。则事已垂成。瞽亦恐难容他。
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前既言君子不教子之义。而却恐天下后世为人父兄者。远其子弟。弃而不教。故于此又以养之之道。反复言之。盖责善则夷矣。不教则弃之。惟此养之一字。既无患乎相夷。又不事乎弃之。孟子之拈出此义。以继公孙丑问答之后者。可见圣贤为天下深虑也欤。
来教尽好
本庵集卷四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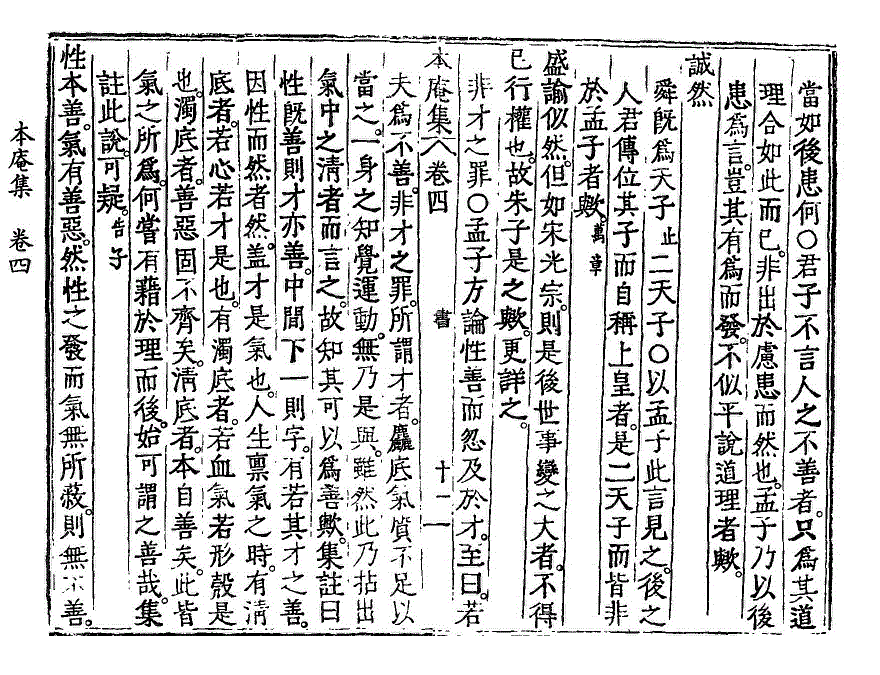 当如后患何○君子不言人之不善者。只为其道理合如此而已。非出于虑患而然也。孟子乃以后患为言。岂其有为而发。不似平说道理者欤。
当如后患何○君子不言人之不善者。只为其道理合如此而已。非出于虑患而然也。孟子乃以后患为言。岂其有为而发。不似平说道理者欤。诚然
舜既为天子(止)二天子○以孟子此言见之。后之人君传位其子而自称上皇者。是二天子而皆非于孟子者欤。(万章)
盛谕似然。但如宋光宗。则是后世事变之大者。不得已行权也。故朱子是之欤。更详之。
非才之罪○孟子方论性善而忽及于才。至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所谓才者。粗底气质不足以当之。一身之知觉运动。无乃是与。虽然此乃拈出气中之清者而言之。故知其可以为善欤。集注曰性既善则才亦善。中间下一则字。有若其才之善。因性而然者然。盖才是气也。人生禀气之时。有清底者。若心若才是也。有浊底者。若血气若形壳是也。浊底者。善恶固不齐矣。清底者。本自善矣。此皆气之所为。何尝有藉于理而后。始可谓之善哉。集注此说。可疑。(告子)
性本善。气有善恶。然性之发而气无所蔽。则无不善。
本庵集卷四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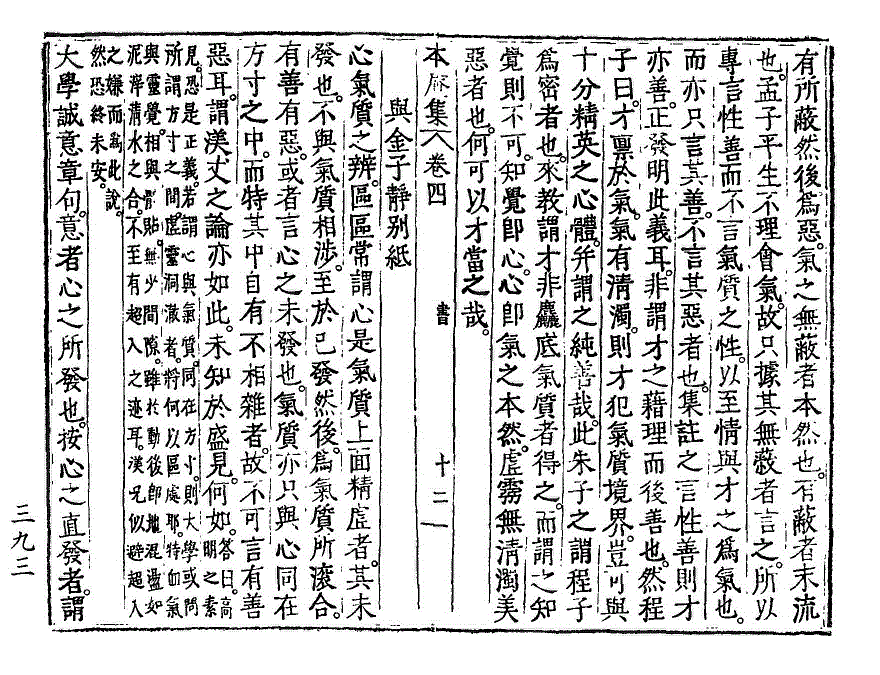 有所蔽然后为恶。气之无蔽者本然也。有蔽者末流也。孟子平生不理会气。故只据其无蔽者言之。所以专言性善而不言气质之性。以至情与才之为气也。而亦只言其善。不言其恶者也。集注之言性善则才亦善。正发明此义耳。非谓才之藉理而后善也。然程子曰。才禀于气。气有清浊。则才犯气质境界。岂可与十分精英之心体。并谓之纯善哉。此朱子之谓程子为密者也。来教谓才非粗底气质者得之。而谓之知觉则不可。知觉即心。心即气之本然。虚灵无清浊美恶者也。何可以才当之哉。
有所蔽然后为恶。气之无蔽者本然也。有蔽者末流也。孟子平生不理会气。故只据其无蔽者言之。所以专言性善而不言气质之性。以至情与才之为气也。而亦只言其善。不言其恶者也。集注之言性善则才亦善。正发明此义耳。非谓才之藉理而后善也。然程子曰。才禀于气。气有清浊。则才犯气质境界。岂可与十分精英之心体。并谓之纯善哉。此朱子之谓程子为密者也。来教谓才非粗底气质者得之。而谓之知觉则不可。知觉即心。心即气之本然。虚灵无清浊美恶者也。何可以才当之哉。与金子静别纸
心气质之辨。区区常谓心是气质上面精虚者。其未发也。不与气质相涉。至于已发然后。为气质所滚合。有善有恶。或者言心之未发也。气质亦只与心同在方寸之中。而特其中自有不相杂者。故不可言有善恶耳。谓渼丈之论亦如此。未知于盛见。何如。(答曰。高明之素见。恐是正义。若谓心与气质。同在方寸。则大学或问所谓方寸之间。虚灵洞澈者。将何以区处耶。特血气与灵觉。相与体贴。无少间隙。虽于动后即地混荡如泥滓清水之合。不至有超入之迹耳。渼兄似避超入之嫌而为此说。然恐终未安。)
大学诚意章句。意者心之所发也。按心之直发者。谓
本庵集卷四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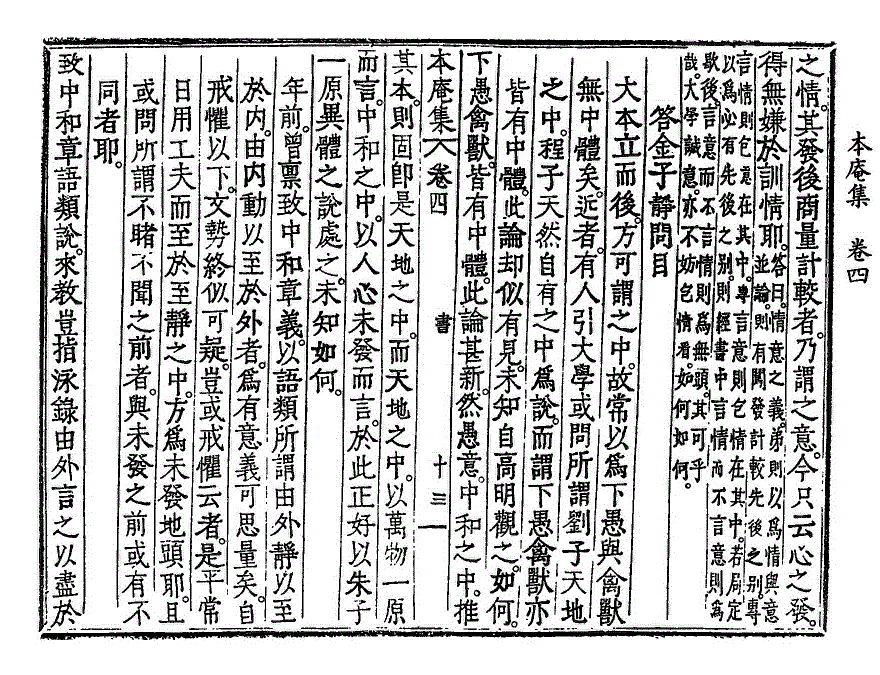 之情。其发后商量计较者。乃谓之意。今只云心之发。得无嫌于训情耶。(答曰。情意之义。弟则以为情与意并论。则有闯发计较先后之别。专言情则包意在其中。专言意则包情在其中。若局定以为必有先后之别。则经书中言情而不言意则为歇后。言意而不言情则为无头。其可乎哉。大学诚意。亦不妨包情看。如何如何。)
之情。其发后商量计较者。乃谓之意。今只云心之发。得无嫌于训情耶。(答曰。情意之义。弟则以为情与意并论。则有闯发计较先后之别。专言情则包意在其中。专言意则包情在其中。若局定以为必有先后之别。则经书中言情而不言意则为歇后。言意而不言情则为无头。其可乎哉。大学诚意。亦不妨包情看。如何如何。)答金子静问目
大本立而后。方可谓之中。故常以为下愚与禽兽无中体矣。近者。有人引大学或问所谓刘子天地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为说。而谓下愚禽兽亦皆有中体。此论却似有见。未知自高明观之。如何。
下愚禽兽。皆有中体。此论甚新。然愚意。中和之中。推其本。则固即是天地之中。而天地之中。以万物一原而言。中和之中。以人心未发而言。于此正好以朱子一原异体之说处之。未知如何。
年前。曾禀致中和章义。以语类所谓由外静以至于内。由内动以至于外者。为有意义可思量矣。自戒惧以下。文势终似可疑。岂或戒惧云者。是平常日用工夫而至于至静之中。方为未发地头耶。且或问所谓不睹不闻之前者。与未发之前或有不同者耶。
致中和章语类说。来教岂指泳录由外言之以尽于
本庵集卷四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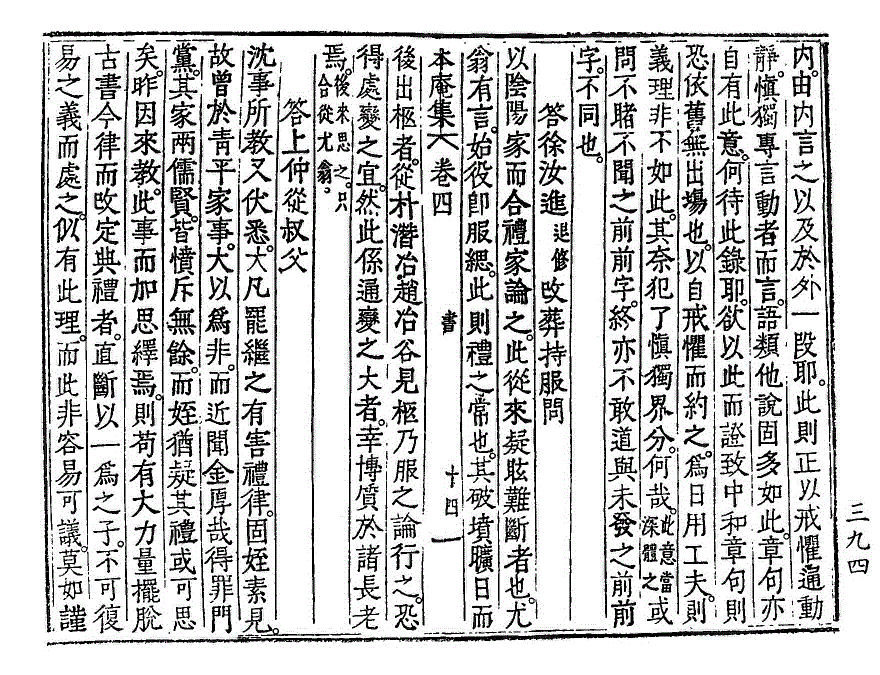 内。由内言之以及于外一段耶。此则正以戒惧通动静。慎独专言动者而言。语类他说固多如此。章句亦自有此意。何待此录耶。欲以此而證致中和章句则恐依旧无出场也。以自戒惧而约之。为日用工夫。则义理非不如此。其奈犯了慎独界分。何哉。(此意当深体之。)或问不睹不闻之前前字。终亦不敢道与未发之前前字。不同也。
内。由内言之以及于外一段耶。此则正以戒惧通动静。慎独专言动者而言。语类他说固多如此。章句亦自有此意。何待此录耶。欲以此而證致中和章句则恐依旧无出场也。以自戒惧而约之。为日用工夫。则义理非不如此。其奈犯了慎独界分。何哉。(此意当深体之。)或问不睹不闻之前前字。终亦不敢道与未发之前前字。不同也。答徐汝进(退修)改葬持服问
以阴阳家而合礼家论之。此从来疑眩难断者也。尤翁有言。始役即服缌。此则礼之常也。其破坟旷日而后出柩者。从朴潜冶,赵冶谷见柩乃服之论行之。恐得处变之宜。然此系通变之大者。幸博质于诸长老焉。(后来思之。只合从尤翁。)
答上仲从叔父
沈事所教又伏悉。大凡罢继之有害礼律。固侄素见。故曾于青平家事。大以为非。而近闻金厚哉得罪门党。其家两儒贤。皆愤斥无馀。而侄犹疑其礼或可思矣。昨因来教。此事而加思绎焉。则苟有大力量摆脱古书今律而改定典礼者。直断以一为之子。不可复易之义而处之。似有此理。而此非容易可议。莫如谨
本庵集卷四 第 3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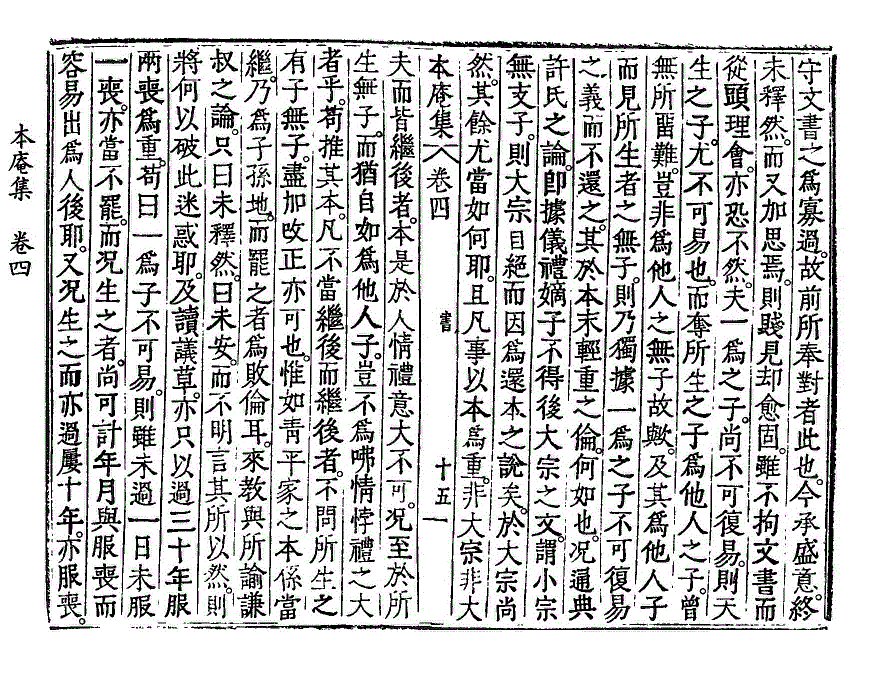 守文书之为寡过。故前所奉对者此也。今承盛意。终未释然。而又加思焉。则贱见却愈固。虽不拘文书而从头理会。亦恐不然。夫一为之子。尚不可复易。则天生之子。尤不可易也。而夺所生之子为他人之子。曾无所留难。岂非为他人之无子故欤。及其为他人子而见所生者之无子。则乃独据一为之子不可复易之义而不还之。其于本末轻重之伦。何如也。况通典许氏之论。即据仪礼嫡子不得后大宗之文。谓小宗无支子。则大宗自绝而因为还本之说矣。于大宗尚然。其馀尤当如何耶。且凡事以本为重。非大宗非大夫而皆继后者。本是于人情礼意大不可。况至于所生无子。而犹自如为他人子。岂不为咈情悖礼之大者乎。苟推其本。凡不当继后而继后者。不问所生之有子无子。尽加改正亦可也。惟如青平家之本系当继。乃为子孙地。而罢之者为败伦耳。来教与所谕谦叔之论。只曰未释然。曰未安。而不明言其所以然。则将何以破此迷惑耶。及读议草。亦只以过三十年服两丧为重。苟曰一为子不可易。则虽未过一日未服一丧。亦当不罢。而况生之者。尚可计年月与服丧而容易出为人后耶。又况生之而亦过屡十年。亦服丧。
守文书之为寡过。故前所奉对者此也。今承盛意。终未释然。而又加思焉。则贱见却愈固。虽不拘文书而从头理会。亦恐不然。夫一为之子。尚不可复易。则天生之子。尤不可易也。而夺所生之子为他人之子。曾无所留难。岂非为他人之无子故欤。及其为他人子而见所生者之无子。则乃独据一为之子不可复易之义而不还之。其于本末轻重之伦。何如也。况通典许氏之论。即据仪礼嫡子不得后大宗之文。谓小宗无支子。则大宗自绝而因为还本之说矣。于大宗尚然。其馀尤当如何耶。且凡事以本为重。非大宗非大夫而皆继后者。本是于人情礼意大不可。况至于所生无子。而犹自如为他人子。岂不为咈情悖礼之大者乎。苟推其本。凡不当继后而继后者。不问所生之有子无子。尽加改正亦可也。惟如青平家之本系当继。乃为子孙地。而罢之者为败伦耳。来教与所谕谦叔之论。只曰未释然。曰未安。而不明言其所以然。则将何以破此迷惑耶。及读议草。亦只以过三十年服两丧为重。苟曰一为子不可易。则虽未过一日未服一丧。亦当不罢。而况生之者。尚可计年月与服丧而容易出为人后耶。又况生之而亦过屡十年。亦服丧。本庵集卷四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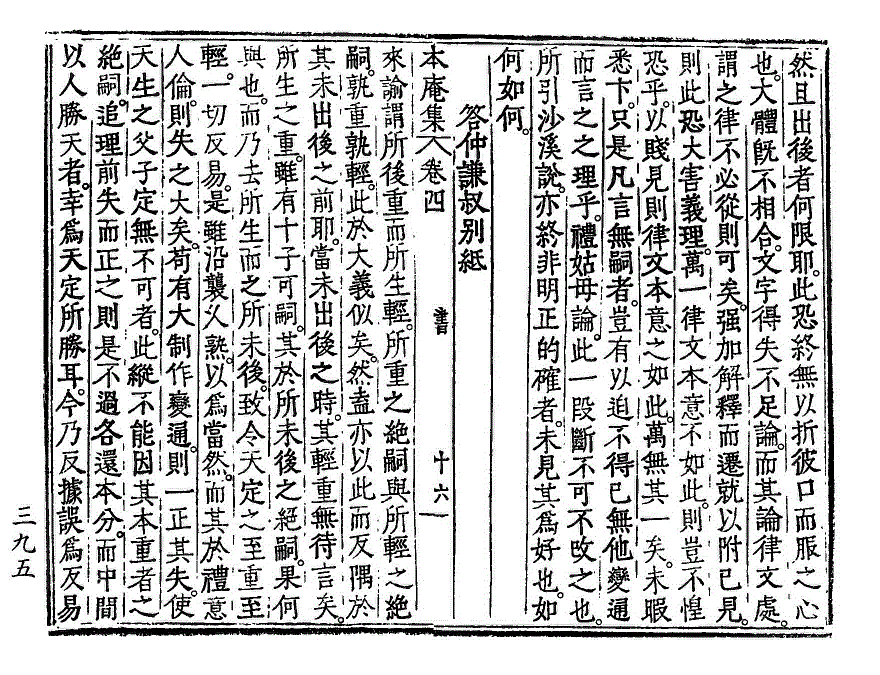 然且出后者何限耶。此恐终无以折彼口而服之心也。大体既不相合。文字得失不足论。而其论律文处。谓之律不必从则可矣。强加解释而迁就以附己见。则此恐大害义理。万一律文本意不如此。则岂不惶恐乎。以贱见则律文本意之如此。万无其一矣。未暇悉卞。只是凡言无嗣者。岂有以迫不得已无他变通而言之之理乎。礼姑毋论。此一段断不可不改之也。所引沙溪说。亦终非明正的确者。未见其为好也。如何如何。
然且出后者何限耶。此恐终无以折彼口而服之心也。大体既不相合。文字得失不足论。而其论律文处。谓之律不必从则可矣。强加解释而迁就以附己见。则此恐大害义理。万一律文本意不如此。则岂不惶恐乎。以贱见则律文本意之如此。万无其一矣。未暇悉卞。只是凡言无嗣者。岂有以迫不得已无他变通而言之之理乎。礼姑毋论。此一段断不可不改之也。所引沙溪说。亦终非明正的确者。未见其为好也。如何如何。答仲谦叔别纸
来谕谓所后重而所生轻。所重之绝嗣与所轻之绝嗣。孰重孰轻。此于大义似矣。然盍亦以此而反隅于其未出后之前耶。当未出后之时。其轻重无待言矣。所生之重。虽有十子可嗣。其于所未后之绝嗣。果何与也。而乃去所生而之所未后。致令天定之至重至轻。一切反易。是虽沿袭久熟。以为当然。而其于礼意人伦。则失之大矣。苟有大制作变通。则一正其失。使天生之父子定无不可者。此纵不能因其本重者之绝嗣。追理前失而正之则是不过各还本分。而中间以人胜天者。幸为天定所胜耳。今乃反据误为反易
本庵集卷四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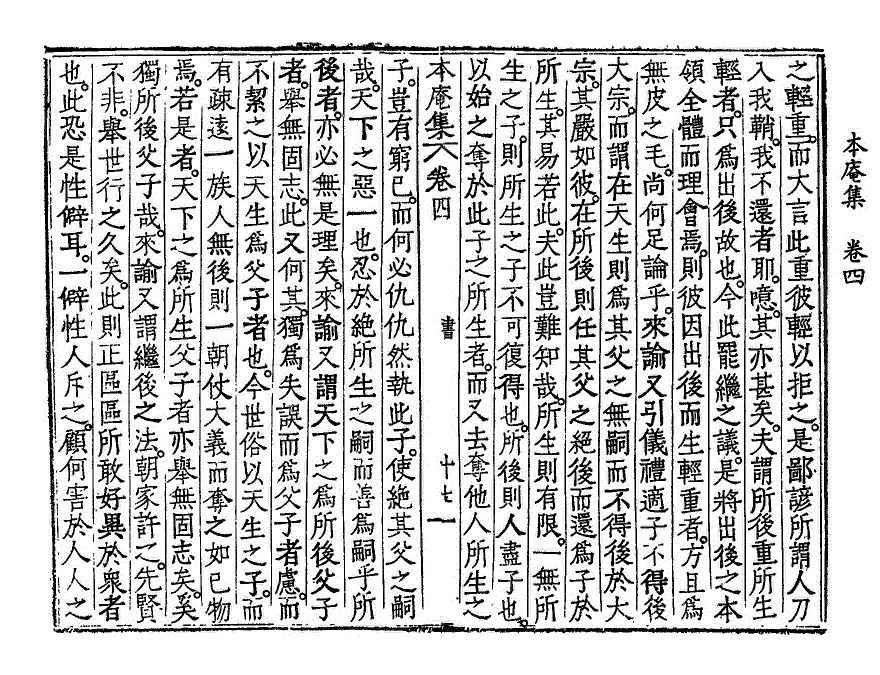 之轻重。而大言此重彼轻以拒之。是鄙谚所谓人刀入我鞘。我不还者耶。噫。其亦甚矣。夫谓所后重所生轻者。只为出后故也。今此罢继之议。是将出后之本领全体而理会焉。则彼因出后而生轻重者。方且为无皮之毛。尚何足论乎。来谕又引仪礼适子不得后大宗。而谓在天生则为其父之无嗣而不得后于大宗。其严如彼。在所后则任其父之绝后而还为子于所生。其易若此。夫此岂难知哉。所生则有限。一无所生之子。则所生之子不可复得也。所后则人尽子也。以始之夺于此子之所生者。而又去夺他人所生之子。岂有穷已。而何必仇仇然执此子。使绝其父之嗣哉。天下之恶一也。忍于绝所生之嗣而善为嗣乎所后者。亦必无是理矣。来谕又谓天下之为所后父子者。举无固志。此又何其独为失误而为父子者虑。而不絜之以天生为父子者也。今世俗以天生之子。而有疏远一族人无后则一朝仗大义而夺之如己物焉。若是者。天下之为所生父子者亦举无固志矣。奚独所后父子哉。来谕又谓继后之法。朝家许之。先贤不非。举世行之久矣。此则正区区所敢好异于众者也。此恐是性僻耳。一僻性人斥之。顾何害于人人之
之轻重。而大言此重彼轻以拒之。是鄙谚所谓人刀入我鞘。我不还者耶。噫。其亦甚矣。夫谓所后重所生轻者。只为出后故也。今此罢继之议。是将出后之本领全体而理会焉。则彼因出后而生轻重者。方且为无皮之毛。尚何足论乎。来谕又引仪礼适子不得后大宗。而谓在天生则为其父之无嗣而不得后于大宗。其严如彼。在所后则任其父之绝后而还为子于所生。其易若此。夫此岂难知哉。所生则有限。一无所生之子。则所生之子不可复得也。所后则人尽子也。以始之夺于此子之所生者。而又去夺他人所生之子。岂有穷已。而何必仇仇然执此子。使绝其父之嗣哉。天下之恶一也。忍于绝所生之嗣而善为嗣乎所后者。亦必无是理矣。来谕又谓天下之为所后父子者。举无固志。此又何其独为失误而为父子者虑。而不絜之以天生为父子者也。今世俗以天生之子。而有疏远一族人无后则一朝仗大义而夺之如己物焉。若是者。天下之为所生父子者亦举无固志矣。奚独所后父子哉。来谕又谓继后之法。朝家许之。先贤不非。举世行之久矣。此则正区区所敢好异于众者也。此恐是性僻耳。一僻性人斥之。顾何害于人人之本庵集卷四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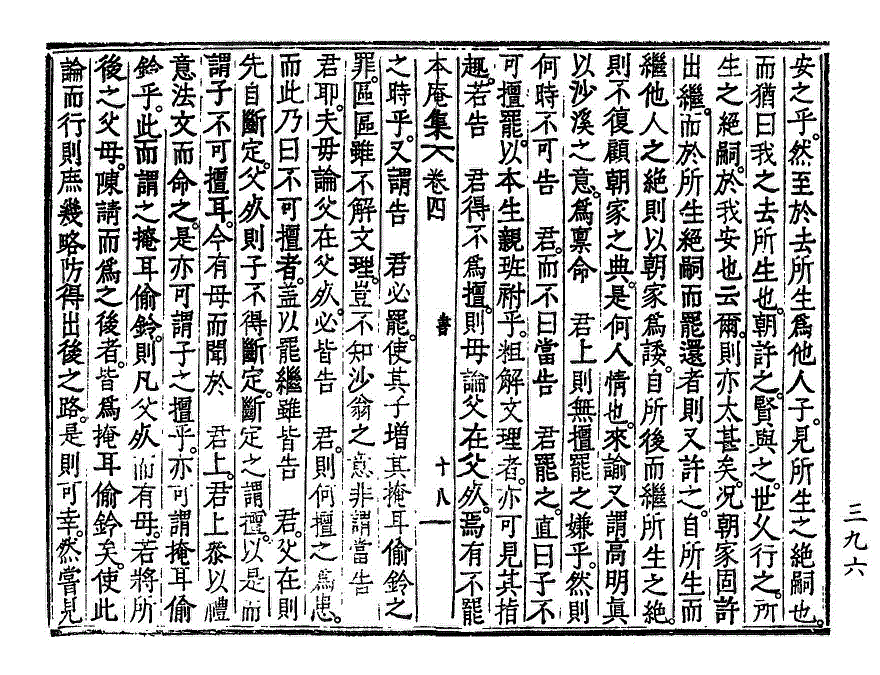 安之乎。然至于去所生为他人子。见所生之绝嗣也。而犹曰我之去所生也。朝许之。贤与之。世久行之。所生之绝嗣。于我安也云尔。则亦太甚矣。况朝家固许出继。而于所生绝嗣而罢还者则又许之。自所生而继他人之绝则以朝家为诿。自所后而继所生之绝。则不复顾朝家之典。是何人情也。来谕又谓高明真以沙溪之意。为禀命 君上则无擅罢之嫌乎。然则何时不可告 君。而不曰当告 君罢之。直曰子不可擅罢。以本生亲班祔乎。粗解文理者。亦可见其指趣。若告 君得不为擅。则毋论父在父死。焉有不罢之时乎。又谓告 君必罢。使其子增其掩耳偷铃之罪。区区虽不解文理。岂不知沙翁之意非谓当告 君耶。夫毋论父在父死。必皆告 君。则何擅之为患。而此乃曰不可擅者。盖以罢继虽皆告 君。父在则先自断定。父死则子不得断定。断定之谓擅。以是而谓子不可擅耳。今有母而闻于 君上。君上参以礼意法文而命之。是亦可谓子之擅乎。亦可谓掩耳偷铃乎。此而谓之掩耳偷铃。则凡父死而有母。若将所后之父母。陈请而为之后者。皆为掩耳偷铃矣。使此论而行则庶几略防得出后之路。是则可幸。然尝见
安之乎。然至于去所生为他人子。见所生之绝嗣也。而犹曰我之去所生也。朝许之。贤与之。世久行之。所生之绝嗣。于我安也云尔。则亦太甚矣。况朝家固许出继。而于所生绝嗣而罢还者则又许之。自所生而继他人之绝则以朝家为诿。自所后而继所生之绝。则不复顾朝家之典。是何人情也。来谕又谓高明真以沙溪之意。为禀命 君上则无擅罢之嫌乎。然则何时不可告 君。而不曰当告 君罢之。直曰子不可擅罢。以本生亲班祔乎。粗解文理者。亦可见其指趣。若告 君得不为擅。则毋论父在父死。焉有不罢之时乎。又谓告 君必罢。使其子增其掩耳偷铃之罪。区区虽不解文理。岂不知沙翁之意非谓当告 君耶。夫毋论父在父死。必皆告 君。则何擅之为患。而此乃曰不可擅者。盖以罢继虽皆告 君。父在则先自断定。父死则子不得断定。断定之谓擅。以是而谓子不可擅耳。今有母而闻于 君上。君上参以礼意法文而命之。是亦可谓子之擅乎。亦可谓掩耳偷铃乎。此而谓之掩耳偷铃。则凡父死而有母。若将所后之父母。陈请而为之后者。皆为掩耳偷铃矣。使此论而行则庶几略防得出后之路。是则可幸。然尝见本庵集卷四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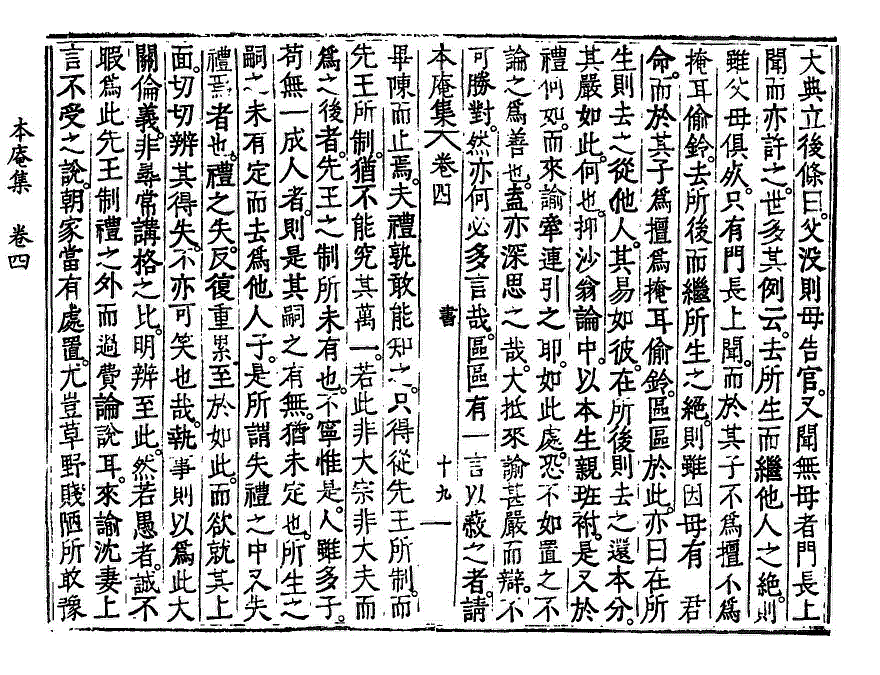 大典立后条曰。父没则母告官。又闻无母者门长上闻而亦许之。世多其例云。去所生而继他人之绝。则虽父母俱死。只有门长上闻。而于其子不为擅不为掩耳偷铃。去所后而继所生之绝。则虽因母有 君命。而于其子为擅为掩耳偷铃。区区于此。亦曰在所生则去之从他人。其易如彼。在所后则去之还本分。其严如此。何也。抑沙翁论中。以本生亲班祔。是又于礼何如。而来谕牵连引之耶。如此处。恐不如置之不论之为善也。盍亦深思之哉。大抵来谕甚严而辩。不可胜对。然亦何必多言哉。区区有一言以蔽之者。请毕陈而止焉。夫礼孰敢能知之。只得从先王所制。而先王所制。犹不能究其万一。若此非大宗非大夫而为之后者。先王之制所未有也。不宁惟是。人虽多子。苟无一成人者。则是其嗣之有无。犹未定也。所生之嗣之未有定而去为他人子。是所谓失礼之中又失礼焉者也。礼之失。反复重累至于如此。而欲就其上面。切切辨其得失。不亦可笑也哉。执事则以为此大关伦义。非寻常讲格之比。明辨至此。然若愚者。诚不暇为此先王制礼之外而过费论说耳。来谕沈妻上言不受之说。朝家当有处置。尤岂草野贱陋所敢豫
大典立后条曰。父没则母告官。又闻无母者门长上闻而亦许之。世多其例云。去所生而继他人之绝。则虽父母俱死。只有门长上闻。而于其子不为擅不为掩耳偷铃。去所后而继所生之绝。则虽因母有 君命。而于其子为擅为掩耳偷铃。区区于此。亦曰在所生则去之从他人。其易如彼。在所后则去之还本分。其严如此。何也。抑沙翁论中。以本生亲班祔。是又于礼何如。而来谕牵连引之耶。如此处。恐不如置之不论之为善也。盍亦深思之哉。大抵来谕甚严而辩。不可胜对。然亦何必多言哉。区区有一言以蔽之者。请毕陈而止焉。夫礼孰敢能知之。只得从先王所制。而先王所制。犹不能究其万一。若此非大宗非大夫而为之后者。先王之制所未有也。不宁惟是。人虽多子。苟无一成人者。则是其嗣之有无。犹未定也。所生之嗣之未有定而去为他人子。是所谓失礼之中又失礼焉者也。礼之失。反复重累至于如此。而欲就其上面。切切辨其得失。不亦可笑也哉。执事则以为此大关伦义。非寻常讲格之比。明辨至此。然若愚者。诚不暇为此先王制礼之外而过费论说耳。来谕沈妻上言不受之说。朝家当有处置。尤岂草野贱陋所敢豫本庵集卷四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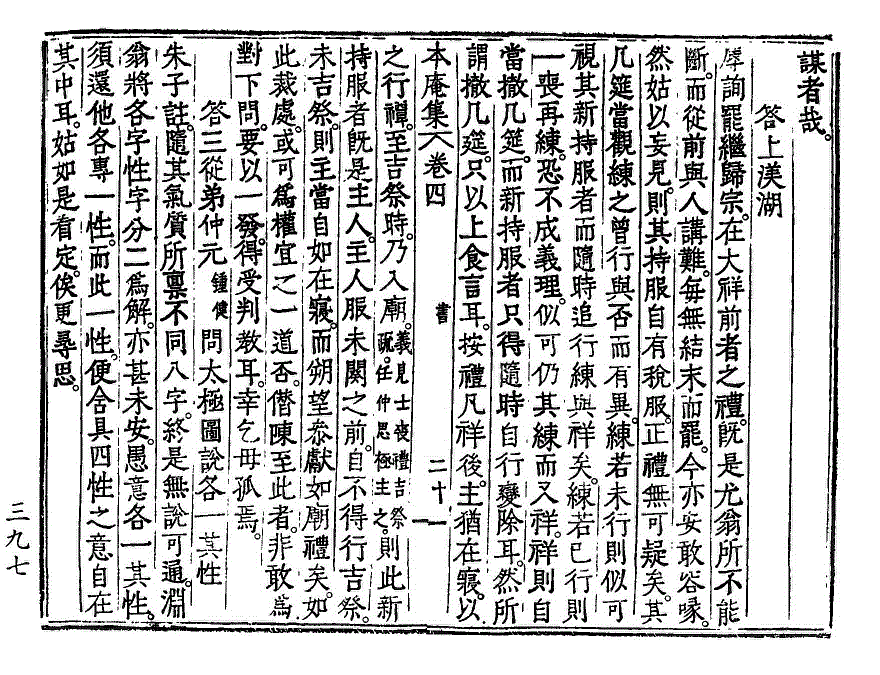 谋者哉。
谋者哉。答上渼湖
辱询罢继归宗。在大祥前者之礼。既是尤翁所不能断。而从前与人讲难。每无结末而罢。今亦安敢容喙。然姑以妄见。则其持服自有税服。正礼无可疑矣。其几筵当观练之曾行与否而有异。练若未行则似可视其新持服者而随时追行练与祥矣。练若已行则一丧再练。恐不成义理。似可仍其练而又祥。祥则自当撤几筵。而新持服者只得随时自行变除耳。然所谓撤几筵。只以上食言耳。按礼凡祥后。主犹在寝。以之行禫。至吉祭时。乃入庙。(义见士丧礼吉发疏。任仲思极主之。)则此新持服者既是主人。主人服未阕之前。自不得行吉祭。未吉祭。则主当自如在寝。而朔望参献如庙礼矣。如此裁处。或可为权宜之一道否。僭陈至此者。非敢为对下问。要以一发。得受判教耳。幸乞毋孤焉。
答三从弟仲元(钟健)问太极图说各一其性
朱子注。随其气质所禀不同八字。终是无说可通。渊翁将各字性字分二为解。亦甚未安。愚意各一其性。须还他各专一性。而此一性。便含具四性之意自在其中耳。姑如是看定。俟更寻思。
本庵集卷四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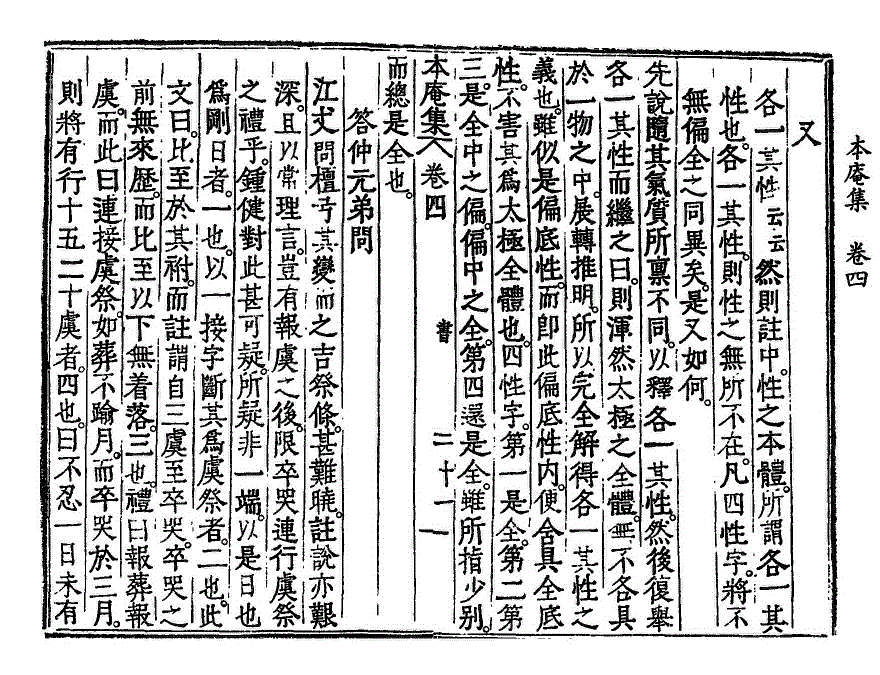 答三从弟仲元(钟健)问太极图说各一其性
答三从弟仲元(钟健)问太极图说各一其性各一其性(云云)然则注中。性之本体。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性之无所不在。凡四性字。将不无偏全之同异矣。是又如何。
先说随其气质所禀不同。以释各一其性。然后复举各一其性而继之曰。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展转推明。所以完全解得各一其性之义也。虽似是偏底性。而即此偏底性内。便含具全底性。不害其为太极全体也。四性字。第一是全。第二第三。是全中之偏。偏中之全。第四还是全。虽所指少别。而总是全也。
答仲元弟问
江丈问檀弓其变而之吉祭条。甚难晓。注说亦艰深。且以常理言。岂有报虞之后。限卒哭连行虞祭之礼乎。钟健对此甚可疑。所疑非一端。以是日也为刚日者。一也。以一接字断其为虞祭者。二也。此文曰。比至于其祔。而注谓自三虞至卒哭。卒哭之前无来历。而比至以下无着落。三也。礼曰报葬报虞。而此曰连接虞祭。如葬不踰月。而卒哭于三月。则将有行十五二十虞者。四也。曰不忍一日未有
本庵集卷四 第 3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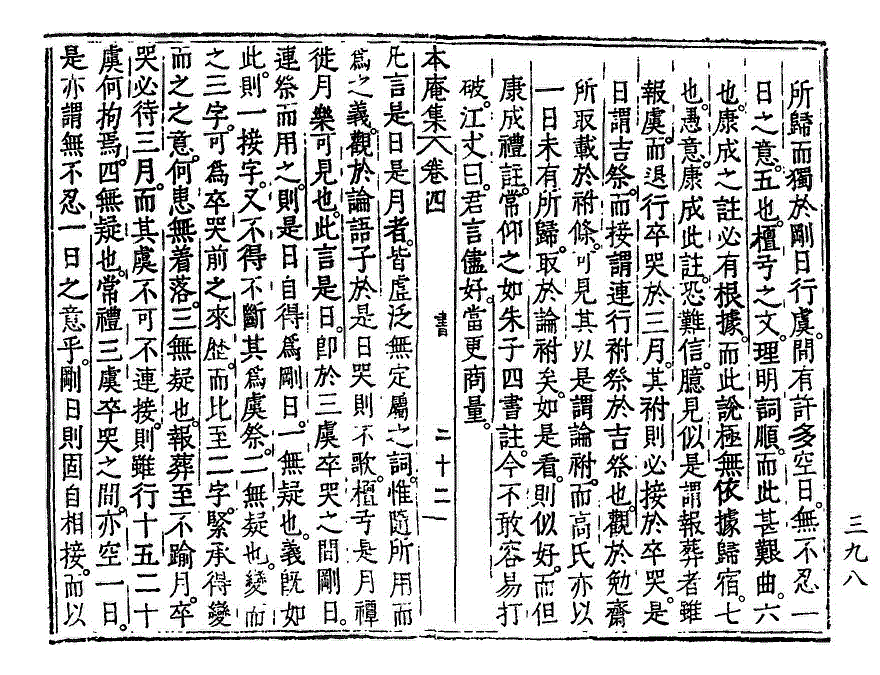 所归而独于刚日行虞。间有许多空日。无不忍一日之意。五也。檀弓之文。理明词顺。而此甚艰曲。六也。康成之注必有根据。而此说极无依据归宿。七也。愚意。康成此注。恐难信。臆见似是谓报葬者虽报虞。而退行卒哭于三月。其祔则必接于卒哭。是日谓吉祭。而接谓连行祔祭于吉祭也。观于勉斋所取载于祔条。可见其以是谓论祔。而高氏亦以一日未有所归。取于论祔矣。如是看。则似好。而但康成礼注。常仰之如朱子四书注。今不敢容易打破。江丈曰。君言尽好。当更商量。
所归而独于刚日行虞。间有许多空日。无不忍一日之意。五也。檀弓之文。理明词顺。而此甚艰曲。六也。康成之注必有根据。而此说极无依据归宿。七也。愚意。康成此注。恐难信。臆见似是谓报葬者虽报虞。而退行卒哭于三月。其祔则必接于卒哭。是日谓吉祭。而接谓连行祔祭于吉祭也。观于勉斋所取载于祔条。可见其以是谓论祔。而高氏亦以一日未有所归。取于论祔矣。如是看。则似好。而但康成礼注。常仰之如朱子四书注。今不敢容易打破。江丈曰。君言尽好。当更商量。凡言是日是月者。皆虚泛无定属之词。惟随所用而为之义。观于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檀弓是月禫徙月乐可见也。此言是日。即于三虞卒哭之间刚日。连祭而用之。则是日自得为刚日。一无疑也。义既如此。则一接字。又不得不断其为虞祭。二无疑也。变而之三字。可为卒哭前之来历。而比至二字。紧承得变而之之意。何患无着落。三无疑也。报葬至不踰月。卒哭必待三月。而其虞不可不连接。则虽行十五二十虞何拘焉。四无疑也。常礼三虞卒哭之间。亦空一日。是亦谓无不忍一日之意乎。刚日则固自相接。而以
本庵集卷四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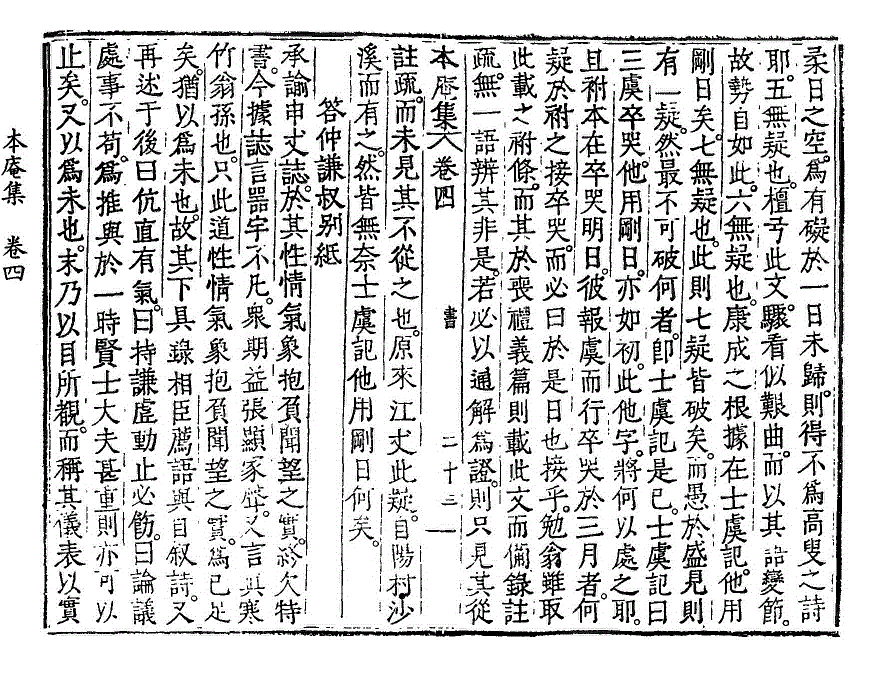 柔日之空。为有碍于一日未归。则得不为高叟之诗耶。五无疑也。檀弓此文。骤看似艰曲。而以其语变节。故势自如此。六无疑也。康成之根据在士虞记。他用刚日矣。七无疑也。此则七疑皆破矣。而愚于盛见则有一疑。然最不可破何者。即士虞记是已。士虞记曰三虞卒哭。他用刚日。亦如初。此他字。将何以处之耶。且祔本在卒哭明日。彼报虞而行卒哭于三月者。何疑于祔之接卒哭。而必曰于是日也接乎。勉翁虽取此载之祔条。而其于丧礼义篇则载此文而备录注疏。无一语辨其非是。若必以通解为證。则只见其从注疏。而未见其不从之也。原来江丈此疑。自阳村,沙溪而有之。然皆无奈士虞记他用刚日何矣。
柔日之空。为有碍于一日未归。则得不为高叟之诗耶。五无疑也。檀弓此文。骤看似艰曲。而以其语变节。故势自如此。六无疑也。康成之根据在士虞记。他用刚日矣。七无疑也。此则七疑皆破矣。而愚于盛见则有一疑。然最不可破何者。即士虞记是已。士虞记曰三虞卒哭。他用刚日。亦如初。此他字。将何以处之耶。且祔本在卒哭明日。彼报虞而行卒哭于三月者。何疑于祔之接卒哭。而必曰于是日也接乎。勉翁虽取此载之祔条。而其于丧礼义篇则载此文而备录注疏。无一语辨其非是。若必以通解为證。则只见其从注疏。而未见其不从之也。原来江丈此疑。自阳村,沙溪而有之。然皆无奈士虞记他用刚日何矣。答仲谦叔别纸
承谕申丈志。于其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终欠特书。今据志言器宇不凡。众期益张显家声。又言真寒竹翁孙也。只此道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为已足矣。犹以为未也。故其下具录相臣荐语与自叙诗。又再述于后曰伉直有气。曰持谦虚动止必饬。曰论议处事不苟。为推与于一时贤士大夫甚重则亦可以止矣。又以为未也。末乃以目所睹。而称其仪表以实
本庵集卷四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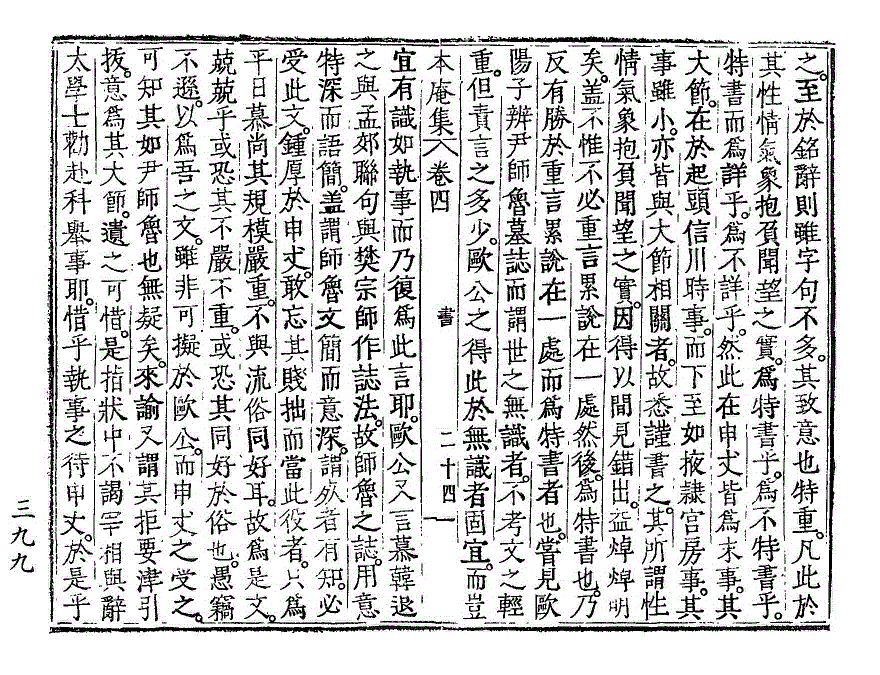 之。至于铭辞则虽字句不多。其致意也特重。凡此于其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为特书乎。为不特书乎。特书而为详乎。为不详乎。然此在申丈皆为末事。其大节。在于起头信川时事。而下至如掖隶宫房事。其事虽小。亦皆与大节相关者。故悉谨书之。其所谓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因得以间见错出。益焯焯明矣。盖不惟不必重言累说在一处然后。为特书也。乃反有胜于重言累说在一处而为特书者也。尝见欧阳子辨尹师鲁墓志而谓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欧公之得此于无识者固宜。而岂宜有识如执事而乃复为此言耶。欧公又言慕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与樊宗师作志法。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谓师鲁文简而意深。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钟厚于申丈。敢忘其贱拙而当此役者。只为平日慕尚其规模严重。不与流俗同好耳。故为是文。兢兢乎或恐其不严不重。或恐其同好于俗也。愚窃不逊。以为吾之文。虽非可拟于欧公。而申丈之受之。可知其如尹师鲁也无疑矣。来谕又谓其拒要津引拔。意为其大节。遗之可惜。是指状中不谒宰相与辞太学士劝赴科举事耶。惜乎执事之待申丈。于是乎
之。至于铭辞则虽字句不多。其致意也特重。凡此于其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为特书乎。为不特书乎。特书而为详乎。为不详乎。然此在申丈皆为末事。其大节。在于起头信川时事。而下至如掖隶宫房事。其事虽小。亦皆与大节相关者。故悉谨书之。其所谓性情气象抱负闻望之实。因得以间见错出。益焯焯明矣。盖不惟不必重言累说在一处然后。为特书也。乃反有胜于重言累说在一处而为特书者也。尝见欧阳子辨尹师鲁墓志而谓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欧公之得此于无识者固宜。而岂宜有识如执事而乃复为此言耶。欧公又言慕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与樊宗师作志法。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谓师鲁文简而意深。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钟厚于申丈。敢忘其贱拙而当此役者。只为平日慕尚其规模严重。不与流俗同好耳。故为是文。兢兢乎或恐其不严不重。或恐其同好于俗也。愚窃不逊。以为吾之文。虽非可拟于欧公。而申丈之受之。可知其如尹师鲁也无疑矣。来谕又谓其拒要津引拔。意为其大节。遗之可惜。是指状中不谒宰相与辞太学士劝赴科举事耶。惜乎执事之待申丈。于是乎本庵集卷四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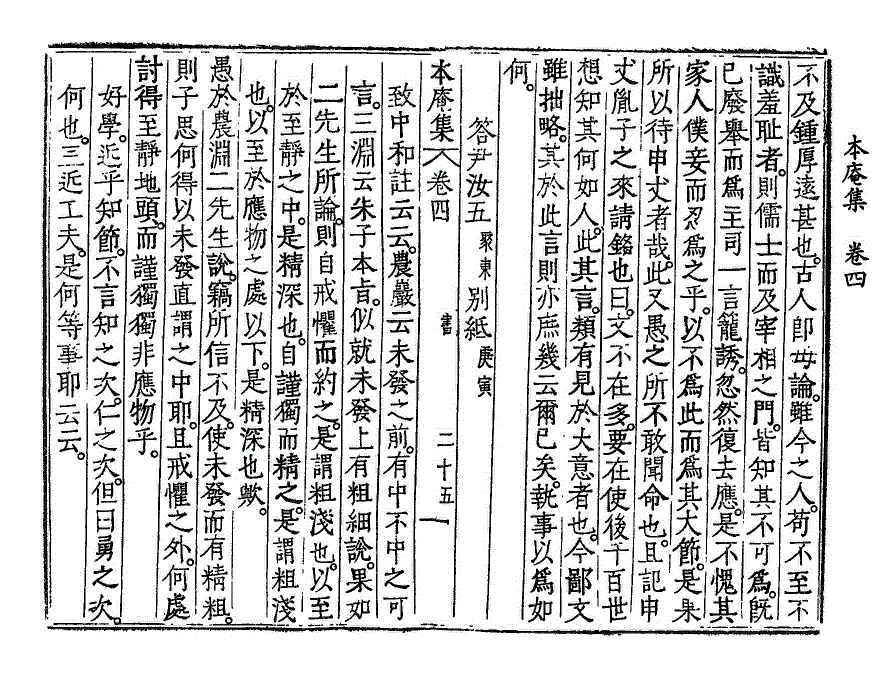 不及钟厚远甚也。古人即毋论。虽今之人。苟不至不识羞耻者。则儒士而及宰相之门。皆知其不可为。既已废举而为主司一言笼诱。忽然复去应。是不愧其家人仆妾而忍为之乎。以不为此而为其大节。是果所以待申丈者哉。此又愚之所不敢闻命也。且记申丈胤子之来请铭也曰。文不在多。要在使后千百世想知其何如人。此其言。类有见于大意者也。今鄙文虽拙略。其于此言则亦庶几云尔已矣。执事以为如何。
不及钟厚远甚也。古人即毋论。虽今之人。苟不至不识羞耻者。则儒士而及宰相之门。皆知其不可为。既已废举而为主司一言笼诱。忽然复去应。是不愧其家人仆妾而忍为之乎。以不为此而为其大节。是果所以待申丈者哉。此又愚之所不敢闻命也。且记申丈胤子之来请铭也曰。文不在多。要在使后千百世想知其何如人。此其言。类有见于大意者也。今鄙文虽拙略。其于此言则亦庶几云尔已矣。执事以为如何。答尹汝五(聚东)别纸(庚寅)
致中和注云云。农岩云未发之前。有中不中之可言。三渊云朱子本旨。似就未发上有粗细说。果如二先生所论。则自戒惧而约之。是谓粗浅也。以至于至静之中。是精深也。自谨独而精之。是谓粗浅也。以至于应物之处以下。是精深也欤。
愚于农渊二先生说。窃所信不及。使未发而有精粗。则子思何得以未发直谓之中耶。且戒惧之外。何处讨得至静地头。而谨独独非应物乎。
好学。近乎知节。不言知之次。仁之次。但曰勇之次。何也。三近工夫。是何等事耶云云。
本庵集卷四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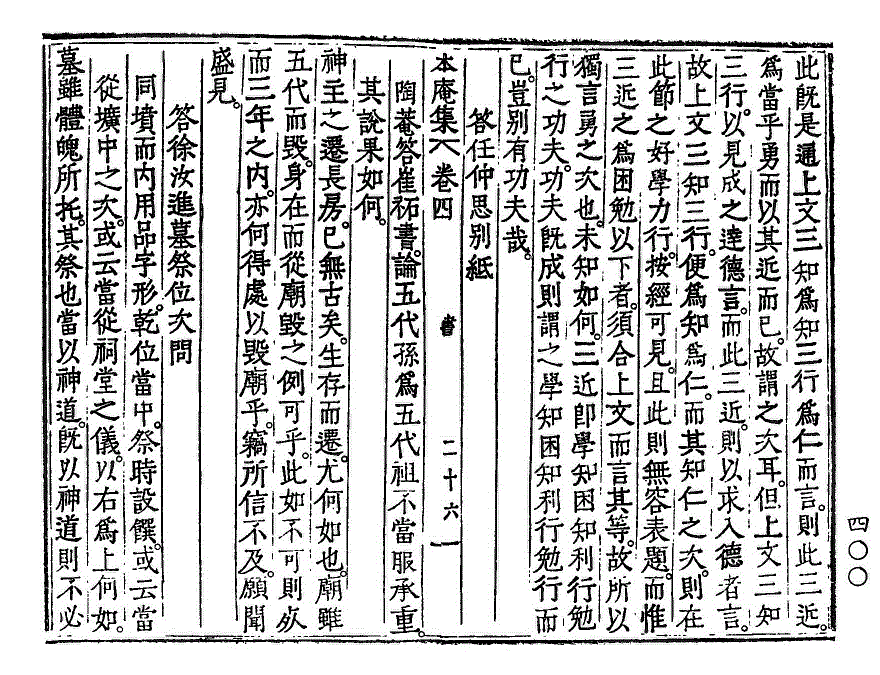 此既是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而言。则此三近。为当乎勇而以其近而已。故谓之次耳。但上文三知三行。以见成之达德言。而此三近。则以求入德者言。故上文三知三行。便为知为仁。而其知仁之次。则在此节之好学力行。按经可见。且此则无容表题。而惟三近之为困勉以下者。须合上文而言其等。故所以独言勇之次也。未知如何。三近即学知困知利行勉行之功夫。功夫既成则谓之学知困知利行勉行而已。岂别有功夫哉。
此既是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而言。则此三近。为当乎勇而以其近而已。故谓之次耳。但上文三知三行。以见成之达德言。而此三近。则以求入德者言。故上文三知三行。便为知为仁。而其知仁之次。则在此节之好学力行。按经可见。且此则无容表题。而惟三近之为困勉以下者。须合上文而言其等。故所以独言勇之次也。未知如何。三近即学知困知利行勉行之功夫。功夫既成则谓之学知困知利行勉行而已。岂别有功夫哉。答任仲思别纸
陶庵答崔祏书。论五代孙为五代祖不当服承重。其说果如何。
神主之迁长房。已无古矣。生存而迁。尤何如也。庙虽五代而毁。身在而从庙毁之例可乎。此如不可则死而三年之内。亦何得处以毁庙乎。窃所信不及。愿闻盛见。
答徐汝进墓祭位次问
同坟而内用品字形。乾位当中。祭时设馔。或云当从圹中之次。或云当从祠堂之仪。以右为上何如。
墓虽体魄所托。其祭也当以神道。既以神道则不必
本庵集卷四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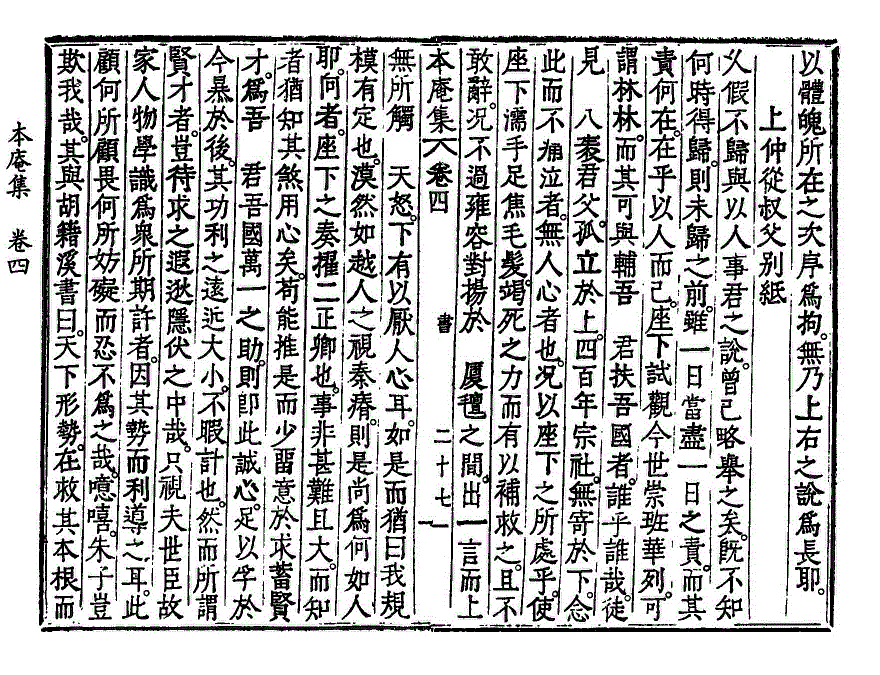 以体魄所在之次序为拘。无乃上右之说为长耶。
以体魄所在之次序为拘。无乃上右之说为长耶。上仲从叔父别纸
久假不归与以人事君之说。曾已略举之矣。既不知何时得归。则未归之前。虽一日当尽一日之责。而其责何在。在乎以人而已。座下试观今世崇班华列。可谓林林。而其可与辅吾 君扶吾国者。谁乎谁哉。徒见 八帙君父。孤立于上。四百年宗社。无寄于下。念此而不痛泣者。无人心者也。况以座下之所处乎。使座下濡手足焦毛发。竭死之力而有以补救之。且不敢辞。况不过雍容对扬于 厦毡之间。出一言而上无所触 天怒。下有以厌人心耳。如是而犹曰我规模有定也。漠然如越人之视秦瘠。则是尚为何如人耶。向者。座下之奏擢二正卿也。事非甚难且大。而知者犹知其煞用心矣。苟能推是而少留意于求蓄贤才。为吾 君吾国万一之助。则即此诚心。足以孚于今暴于后。其功利之远近大小。不暇计也。然而所谓贤才者。岂待求之遐逖隐伏之中哉。只视夫世臣故家人物学识为众所期许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耳。此顾何所顾畏何所妨碍而忍不为之哉。噫嘻。朱子岂欺我哉。其与胡籍溪书曰。天下形势。在救其本根而
本庵集卷四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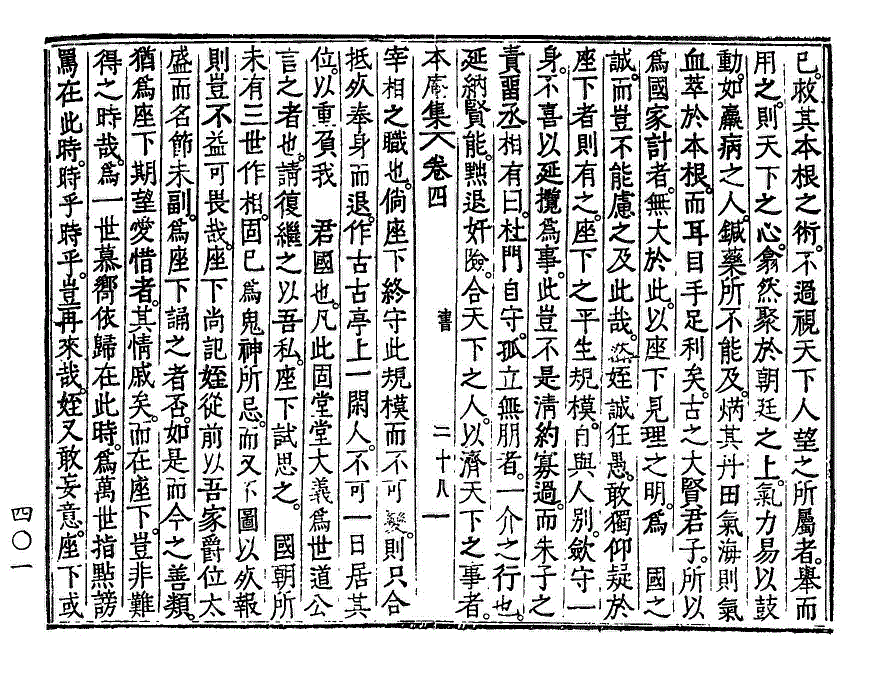 已。救其本根之术。不过视天下人望之所属者。举而用之。则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气力易以鼓动。如羸病之人。针药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气海则气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古之大贤君子。所以为国家计者。无大于此。以座下见理之明。为 国之诚。而岂不能虑之及此哉。然侄诚狂愚。敢独仰疑于座下者则有之。座下之平生规模。自与人别。敛守一身。不喜以延揽为事。此岂不是清约寡过。而朱子之责留丞相有曰。杜门自守。孤立无朋者。一介之行也。延纳贤能。黜退奸险。合天下之人。以济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职也。倘座下终守此规模而不可变。则只合抵死奉身而退。作古古亭上一闲人。不可一日居其位。以重负我 君国也。凡此固堂堂大义为世道公言之者也。请复继之以吾私。座下试思之。 国朝所未有三世作相。固已为鬼神所忌。而又不图以死报则岂不益可畏哉。座下尚记侄从前以吾家爵位太盛而名节未副。为座下诵之者否。如是而今之善类。犹为座下期望爱惜者。其情戚矣。而在座下。岂非难得之时哉。为一世慕向依归在此时。为万世指点谤骂在此时。时乎时乎。岂再来哉。侄又敢妄意。座下或
已。救其本根之术。不过视天下人望之所属者。举而用之。则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气力易以鼓动。如羸病之人。针药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气海则气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古之大贤君子。所以为国家计者。无大于此。以座下见理之明。为 国之诚。而岂不能虑之及此哉。然侄诚狂愚。敢独仰疑于座下者则有之。座下之平生规模。自与人别。敛守一身。不喜以延揽为事。此岂不是清约寡过。而朱子之责留丞相有曰。杜门自守。孤立无朋者。一介之行也。延纳贤能。黜退奸险。合天下之人。以济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职也。倘座下终守此规模而不可变。则只合抵死奉身而退。作古古亭上一闲人。不可一日居其位。以重负我 君国也。凡此固堂堂大义为世道公言之者也。请复继之以吾私。座下试思之。 国朝所未有三世作相。固已为鬼神所忌。而又不图以死报则岂不益可畏哉。座下尚记侄从前以吾家爵位太盛而名节未副。为座下诵之者否。如是而今之善类。犹为座下期望爱惜者。其情戚矣。而在座下。岂非难得之时哉。为一世慕向依归在此时。为万世指点谤骂在此时。时乎时乎。岂再来哉。侄又敢妄意。座下或本庵集卷四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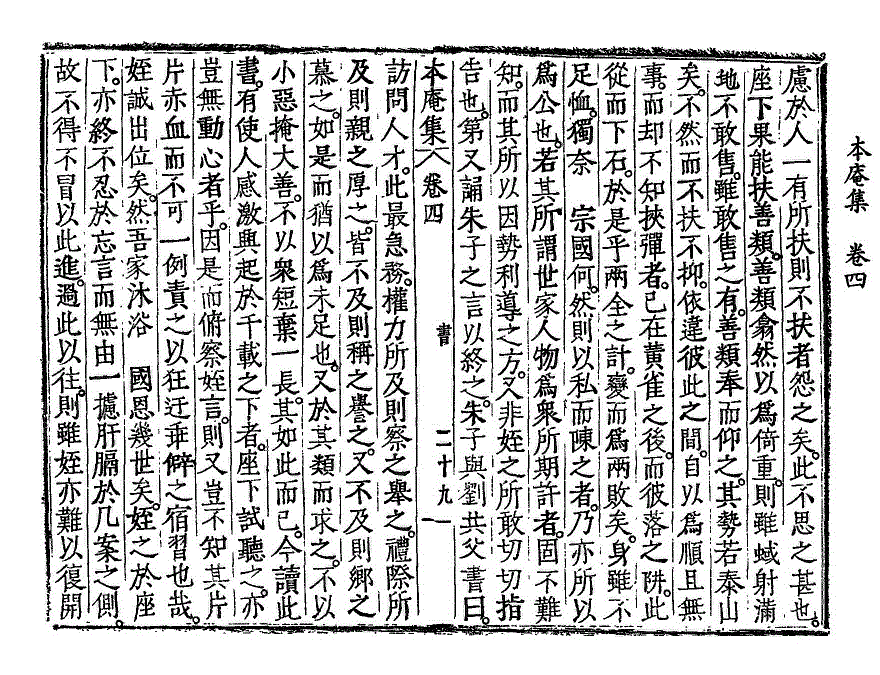 虑于人一有所扶则不扶者怨之矣。此不思之甚也。座下果能扶善类。善类翕然以为倚重。则虽蜮射满地不敢售。虽敢售之有。善类奉而仰之。其势若泰山矣。不然而不扶不抑。依违彼此之间。自以为顺且无事。而却不知挟弹者。已在黄雀之后。而彼落之阱。此从而下石。于是乎两全之计。变而为两败矣。身虽不足恤。独奈 宗国何。然则以私而陈之者。乃亦所以为公也。若其所谓世家人物为众所期许者。固不难知。而其所以因势利导之方。又非侄之所敢切切指告也。第又诵朱子之言以终之。朱子与刘共父书曰。访问人才。此最急务。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乡之慕之。如是而犹以为未足也。又于其类而求之。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其如此而已。今读此书。有使人感激兴起于千载之下者。座下试听之。亦岂无动心者乎。因是而俯察侄言。则又岂不知其片片赤血而不可一例责之以狂迂乖僻之宿习也哉。侄诚出位矣。然吾家沐浴 国恩几世矣。侄之于座下。亦终不忍于忘言而无由一摅肝膈于几案之侧。故不得不冒以此进。过此以往。则虽侄亦难以复开
虑于人一有所扶则不扶者怨之矣。此不思之甚也。座下果能扶善类。善类翕然以为倚重。则虽蜮射满地不敢售。虽敢售之有。善类奉而仰之。其势若泰山矣。不然而不扶不抑。依违彼此之间。自以为顺且无事。而却不知挟弹者。已在黄雀之后。而彼落之阱。此从而下石。于是乎两全之计。变而为两败矣。身虽不足恤。独奈 宗国何。然则以私而陈之者。乃亦所以为公也。若其所谓世家人物为众所期许者。固不难知。而其所以因势利导之方。又非侄之所敢切切指告也。第又诵朱子之言以终之。朱子与刘共父书曰。访问人才。此最急务。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乡之慕之。如是而犹以为未足也。又于其类而求之。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其如此而已。今读此书。有使人感激兴起于千载之下者。座下试听之。亦岂无动心者乎。因是而俯察侄言。则又岂不知其片片赤血而不可一例责之以狂迂乖僻之宿习也哉。侄诚出位矣。然吾家沐浴 国恩几世矣。侄之于座下。亦终不忍于忘言而无由一摅肝膈于几案之侧。故不得不冒以此进。过此以往。则虽侄亦难以复开本庵集卷四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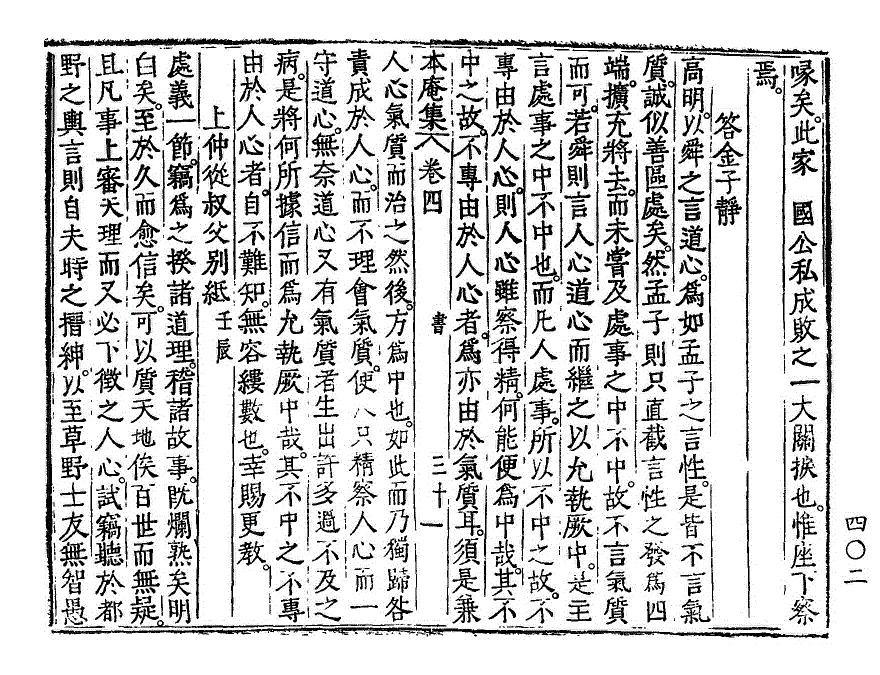 喙矣。此家 国公私成败之一大关捩也。惟座下察焉。
喙矣。此家 国公私成败之一大关捩也。惟座下察焉。答金子静
高明。以舜之言道心。为如孟子之言性。是皆不言气质。诚似善区处矣。然孟子则只直截言性之发为四端。扩充将去。而未尝及处事之中不中。故不言气质而可。若舜则言人心道心而继之以允执厥中。是主言处事之中不中也。而凡人处事。所以不中之故。不专由于人心。则人心虽察得精。何能便为中哉。其不中之故。不专由于人心者。为亦由于气质耳。须是兼人心气质而治之然后。方为中也。如此而乃独归咎责成于人心。而不理会气质。使人只精察人心而一守道心。无奈道心又有气质者生出许多过不及之病。是将何所据信而为允执厥中哉。其不中之不专由于人心者。自不难知。无容缕数也。幸赐更教。
上仲从叔父别纸(壬辰)
处义一节。窃为之揆诸道理。稽诸故事。既烂熟矣明白矣。至于久而愈信矣。可以质天地俟百世而无疑。且凡事上审天理而又必下徵之人心。试窃听于都野之舆言则自夫时之搢绅。以至草野士友无智愚
本庵集卷四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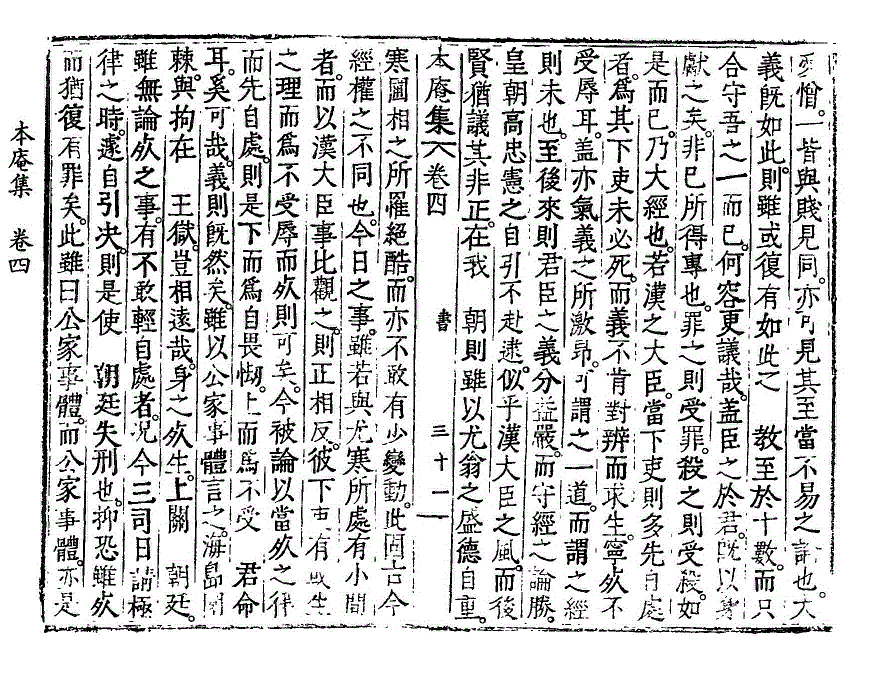 爱憎。一皆与贱见同。亦可见其至当不易之论也。大义既如此。则虽或复有如此之 教至于十数。而只合守吾之一而已。何容更议哉。盖臣之于君。既以身献之矣。非己所得专也。罪之则受罪。杀之则受杀。如是而已。乃大经也。若汉之大臣。当下吏则多先自处者。为其下吏未必死。而义不肯对辨而求生。宁死不受辱耳。盖亦气义之所激昂。可谓之一道。而谓之经则未也。至后来则君臣之义分益严。而守经之论胜。皇朝高忠宪之自引不赴逮。似乎汉大臣之风。而后贤犹议其非正。在我 朝则虽以尤翁之盛德自重。寒圃相之所罹绝酷。而亦不敢有少变动。此固古今经权之不同也。今日之事。虽若与尤寒所处有小间者。而以汉大臣事比观之。则正相反。彼下吏有或生之理而为不受辱而死则可矣。今被论以当死之律而先自处。则是下而为自畏怯。上而为不受 君命耳。奚可哉。义则既然矣。虽以公家事体言之。海岛围棘。与拘在 王狱。岂相远哉。身之死生。上关 朝廷。虽无论死之事。有不敢轻自处者。况今三司日请极律之时。遽自引决。则是使 朝廷失刑也。抑恐虽死而犹复有罪矣。此虽曰公家事体。而公家事体。亦是
爱憎。一皆与贱见同。亦可见其至当不易之论也。大义既如此。则虽或复有如此之 教至于十数。而只合守吾之一而已。何容更议哉。盖臣之于君。既以身献之矣。非己所得专也。罪之则受罪。杀之则受杀。如是而已。乃大经也。若汉之大臣。当下吏则多先自处者。为其下吏未必死。而义不肯对辨而求生。宁死不受辱耳。盖亦气义之所激昂。可谓之一道。而谓之经则未也。至后来则君臣之义分益严。而守经之论胜。皇朝高忠宪之自引不赴逮。似乎汉大臣之风。而后贤犹议其非正。在我 朝则虽以尤翁之盛德自重。寒圃相之所罹绝酷。而亦不敢有少变动。此固古今经权之不同也。今日之事。虽若与尤寒所处有小间者。而以汉大臣事比观之。则正相反。彼下吏有或生之理而为不受辱而死则可矣。今被论以当死之律而先自处。则是下而为自畏怯。上而为不受 君命耳。奚可哉。义则既然矣。虽以公家事体言之。海岛围棘。与拘在 王狱。岂相远哉。身之死生。上关 朝廷。虽无论死之事。有不敢轻自处者。况今三司日请极律之时。遽自引决。则是使 朝廷失刑也。抑恐虽死而犹复有罪矣。此虽曰公家事体。而公家事体。亦是本庵集卷四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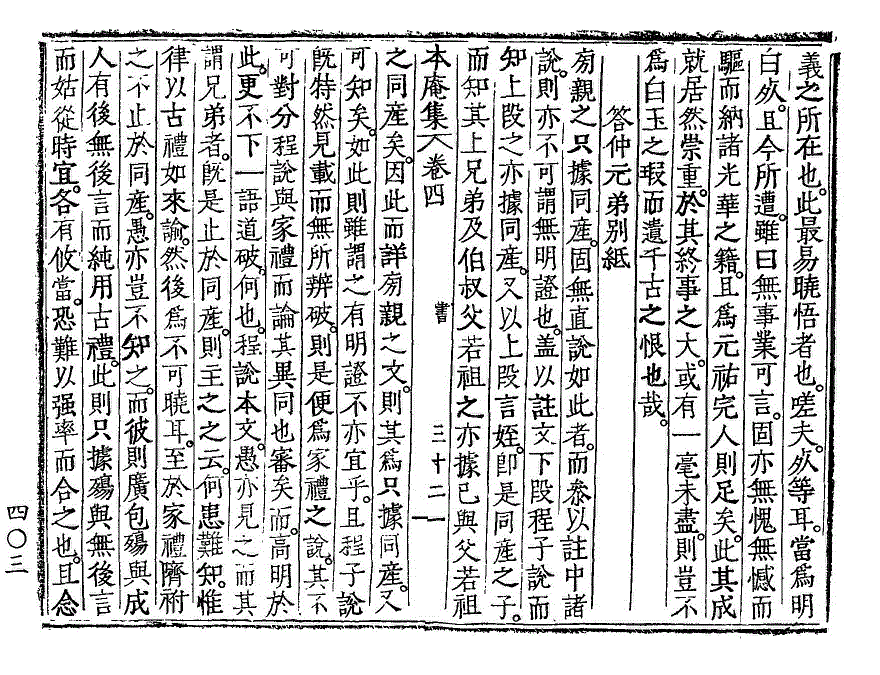 义之所在也。此最易晓悟者也。嗟夫。死等耳。当为明白死。且今所遭。虽曰无事业可言。固亦无愧无憾而驱而纳诸光华之籍。且为元祐完人则足矣。此其成就居然崇重。于其终事之大。或有一毫未尽。则岂不为白玉之瑕而遗千古之恨也哉。
义之所在也。此最易晓悟者也。嗟夫。死等耳。当为明白死。且今所遭。虽曰无事业可言。固亦无愧无憾而驱而纳诸光华之籍。且为元祐完人则足矣。此其成就居然崇重。于其终事之大。或有一毫未尽。则岂不为白玉之瑕而遗千古之恨也哉。答仲元弟别纸
旁亲之只据同产。固无直说如此者。而参以注中诸说。则亦不可谓无明證也。盖以注文下段程子说而知上段之亦据同产。又以上段言侄。即是同产之子。而知其上兄弟及伯叔父若祖之亦据己与父若祖之同产矣。因此而详旁亲之文。则其为只据固产。又可知矣。如此则虽谓之有明證不亦宜乎。且程子说既特然见载而无所辨破。则是便为家礼之说。其不可对分程说与家礼而论其异同也审矣。而高明于此。更不下一语道破。何也。程说本文。愚亦见之。而其谓兄弟者。既是止于同产。则主之之云。何患难知。惟律以古礼如来谕。然后为不可晓耳。至于家礼隮祔之不止于同产。愚亦岂不知之。而彼则广包殇与成人有后无后言而纯用古礼。此则只据殇与无后言而姑从时宜。各有攸当。恐难以强率而合之也。且念
本庵集卷四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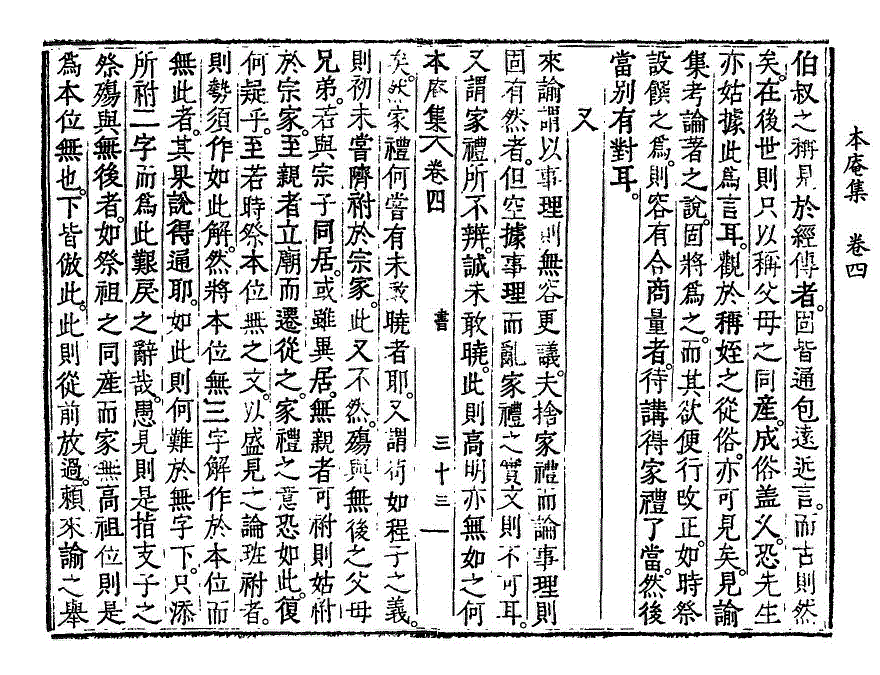 伯叔之称见于经传者。固皆通包远近言。而古则然矣。在后世则只以称父母之同产。成俗盖久。恐先生亦姑据此为言耳。观于称侄之从俗。亦可见矣。见谕集考论著之说。固将为之。而其欲便行改正。如时祭设馔之为。则容有合商量者。待讲得家礼了当。然后当别有对耳。
伯叔之称见于经传者。固皆通包远近言。而古则然矣。在后世则只以称父母之同产。成俗盖久。恐先生亦姑据此为言耳。观于称侄之从俗。亦可见矣。见谕集考论著之说。固将为之。而其欲便行改正。如时祭设馔之为。则容有合商量者。待讲得家礼了当。然后当别有对耳。答仲元弟别纸
来谕谓以事理则无容更议。夫舍家礼而论事理则固有然者。但空据事理而乱家礼之实文则不可耳。又谓家礼所不辨。诚未敢晓。此则高明亦无如之何矣。然家礼何尝有未敢晓者耶。又谓苟如程子之义。则初未尝隮祔于宗家。此又不然。殇与无后之父母兄弟。若与宗子同居。或虽异居。无亲者可祔则姑祔于宗家。至亲者立庙而迁从之。家礼之意恐如此。复何疑乎。至若时祭本位无之文。以盛见之论班祔者。则势须作如此解。然将本位无三字解作于本位而无此者。其果说得通耶。如此则何难于无字下。只添所祔二字而为此艰戾之辞哉。愚见则是指支子之祭殇与无后者。如祭祖之同产而家无高祖位则是为本位无也。下皆仿此。此则从前放过。赖来谕之举
本庵集卷四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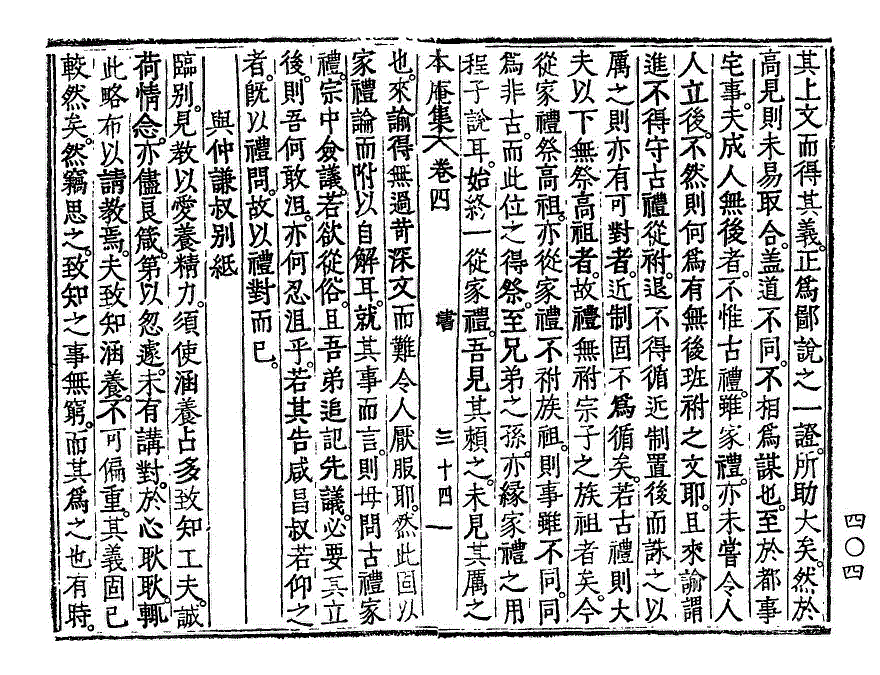 其上文而得其义。正为鄙说之一證。所助大矣。然于高见则未易取合。盖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至于都事宅事。夫成人无后者。不惟古礼。虽家礼亦未尝令人人立后。不然则何为有无后班祔之文耶。且来谕谓进不得守古礼从祔。退不得循近制置后而诛之以厉之则亦有可对者。近制固不为循矣。若古礼则大夫以下无祭高祖者。故礼无祔宗子之族祖者矣。今从家礼祭高祖。亦从家礼不祔族祖。则事虽不同。同为非古。而此位之得祭。至兄弟之孙。亦缘家礼之用程子说耳。始终一从家礼。吾见其赖之。未见其厉之也。来谕得无过苛深文而难令人厌服耶。然此固以家礼论而附以自解耳。就其事而言。则毋问古礼家礼。宗中佥议。若欲从俗。且吾弟追记先议。必要其立后。则吾何敢沮。亦何忍沮乎。若其告咸昌叔若仰之者。既以礼问。故以礼对而已。
其上文而得其义。正为鄙说之一證。所助大矣。然于高见则未易取合。盖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至于都事宅事。夫成人无后者。不惟古礼。虽家礼亦未尝令人人立后。不然则何为有无后班祔之文耶。且来谕谓进不得守古礼从祔。退不得循近制置后而诛之以厉之则亦有可对者。近制固不为循矣。若古礼则大夫以下无祭高祖者。故礼无祔宗子之族祖者矣。今从家礼祭高祖。亦从家礼不祔族祖。则事虽不同。同为非古。而此位之得祭。至兄弟之孙。亦缘家礼之用程子说耳。始终一从家礼。吾见其赖之。未见其厉之也。来谕得无过苛深文而难令人厌服耶。然此固以家礼论而附以自解耳。就其事而言。则毋问古礼家礼。宗中佥议。若欲从俗。且吾弟追记先议。必要其立后。则吾何敢沮。亦何忍沮乎。若其告咸昌叔若仰之者。既以礼问。故以礼对而已。与仲谦叔别纸
临别。见教以爱养精力。须使涵养占多致知工夫。诚荷情念。亦尽良箴。第以匆遽。未有讲对。于心耿耿。辄此略布以请教焉。夫致知涵养。不可偏重。其义固已较然矣。然窃思之。致知之事无穷。而其为之也有时。
本庵集卷四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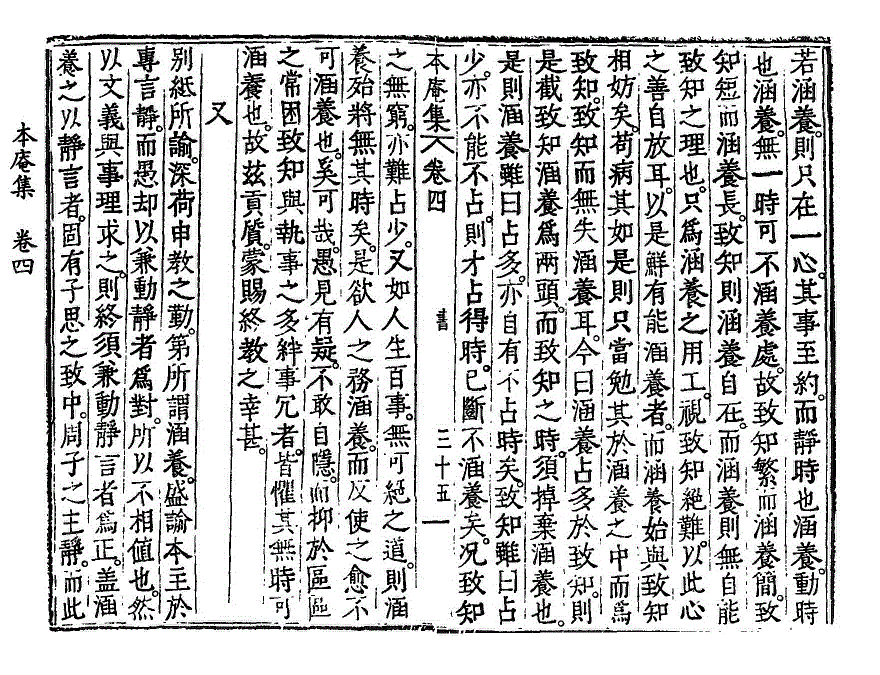 若涵养。则只在一心。其事至约。而静时也涵养。动时也涵养。无一时可不涵养处。故致知繁而涵养简。致知短而涵养长。致知则涵养自在。而涵养则无自能致知之理也。只为涵养之用工。视致知绝难。以此心之善自放耳。以是鲜有能涵养者。而涵养始与致知相妨矣。苟病其如是则只当勉其于涵养之中而为致知。致知而无失涵养耳。今日涵养占多于致知。则是截致知涵养为两头。而致知之时。须掉弃涵养也。是则涵养虽曰占多。亦自有不占时矣。致知虽曰占少。亦不能不占。则才占得时。已断不涵养矣。况致知之无穷。亦难占少。又如人生百事。无可绝之道。则涵养殆将无其时矣。是欲人之务涵养。而反使之愈不可涵养也。奚可哉。愚见有疑。不敢自隐。而抑于区区之常困致知与执事之多绊事冗者。皆惧其无时可涵养也。故玆贡质。蒙赐终教之幸甚。
若涵养。则只在一心。其事至约。而静时也涵养。动时也涵养。无一时可不涵养处。故致知繁而涵养简。致知短而涵养长。致知则涵养自在。而涵养则无自能致知之理也。只为涵养之用工。视致知绝难。以此心之善自放耳。以是鲜有能涵养者。而涵养始与致知相妨矣。苟病其如是则只当勉其于涵养之中而为致知。致知而无失涵养耳。今日涵养占多于致知。则是截致知涵养为两头。而致知之时。须掉弃涵养也。是则涵养虽曰占多。亦自有不占时矣。致知虽曰占少。亦不能不占。则才占得时。已断不涵养矣。况致知之无穷。亦难占少。又如人生百事。无可绝之道。则涵养殆将无其时矣。是欲人之务涵养。而反使之愈不可涵养也。奚可哉。愚见有疑。不敢自隐。而抑于区区之常困致知与执事之多绊事冗者。皆惧其无时可涵养也。故玆贡质。蒙赐终教之幸甚。与仲谦叔别纸
别纸所谕。深荷申教之勤。第所谓涵养。盛谕本主于专言静。而愚却以兼动静者为对。所以不相值也。然以文义与事理求之。则终须兼动静言者为正。盖涵养之以静言者。固有子思之致中。周子之主静。而此
本庵集卷四 第 4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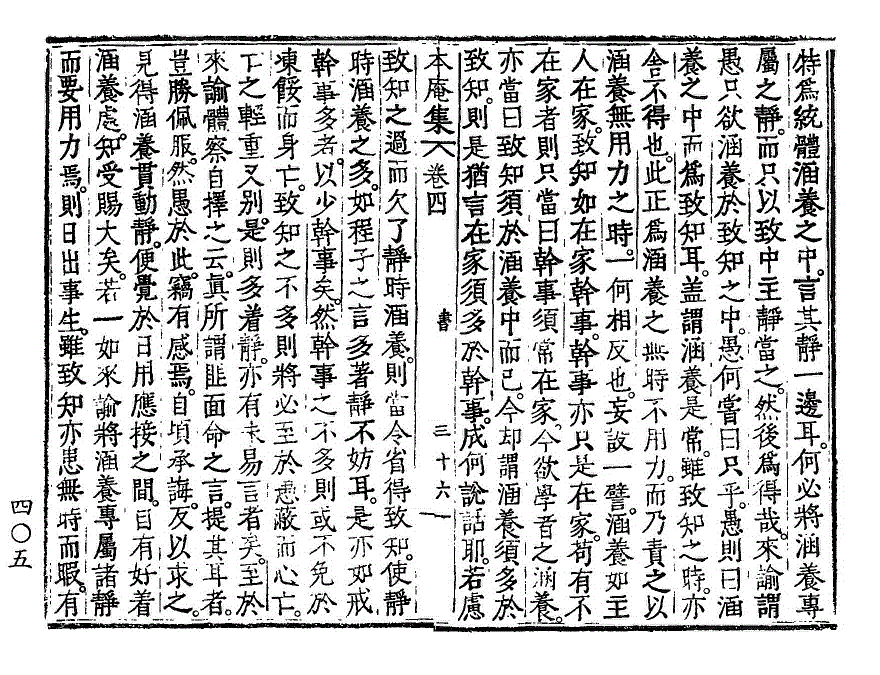 特为统体涵养之中。言其静一边耳。何必将涵养专属之静。而只以致中主静当之。然后为得哉。来谕谓愚只欲涵养于致知之中。愚何尝曰只乎。愚则曰涵养之中而为致知耳。盖谓涵养是常。虽致知之时。亦舍不得也。此正为涵养之无时不用力。而乃责之以涵养无用力之时。一何相反也。妄设一譬。涵养如主人在家。致知如在家干事。干事亦只是在家。苟有不在家者则只当曰干事须常在家。今欲学者之涵养。亦当曰致知须于涵养中而已。今却谓涵养须多于致知。则是犹言在家须多于干事。成何说话耶。若虑致知之过而欠了静时涵养。则当令省得致知。使静时涵养之多。如程子之言多著静不妨耳。是亦如戒干事多者。以少干事矣。然干事之不多则或不免于冻馁而身亡。致知之不多则将必至于愚蔽而心亡。亡之轻重又别。是则多着静。亦有未易言者矣。至于来谕体察自择之云。真所谓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者。岂胜佩服。然愚于此。窃有感焉。自顷承诲。反以求之。见得涵养贯动静。便觉于日用应接之间。自有好着涵养处。知受赐大矣。若一如来谕将涵养专属诸静而要用力焉。则日出事生。虽致知亦患无时而暇。有
特为统体涵养之中。言其静一边耳。何必将涵养专属之静。而只以致中主静当之。然后为得哉。来谕谓愚只欲涵养于致知之中。愚何尝曰只乎。愚则曰涵养之中而为致知耳。盖谓涵养是常。虽致知之时。亦舍不得也。此正为涵养之无时不用力。而乃责之以涵养无用力之时。一何相反也。妄设一譬。涵养如主人在家。致知如在家干事。干事亦只是在家。苟有不在家者则只当曰干事须常在家。今欲学者之涵养。亦当曰致知须于涵养中而已。今却谓涵养须多于致知。则是犹言在家须多于干事。成何说话耶。若虑致知之过而欠了静时涵养。则当令省得致知。使静时涵养之多。如程子之言多著静不妨耳。是亦如戒干事多者。以少干事矣。然干事之不多则或不免于冻馁而身亡。致知之不多则将必至于愚蔽而心亡。亡之轻重又别。是则多着静。亦有未易言者矣。至于来谕体察自择之云。真所谓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者。岂胜佩服。然愚于此。窃有感焉。自顷承诲。反以求之。见得涵养贯动静。便觉于日用应接之间。自有好着涵养处。知受赐大矣。若一如来谕将涵养专属诸静而要用力焉。则日出事生。虽致知亦患无时而暇。有本庵集卷四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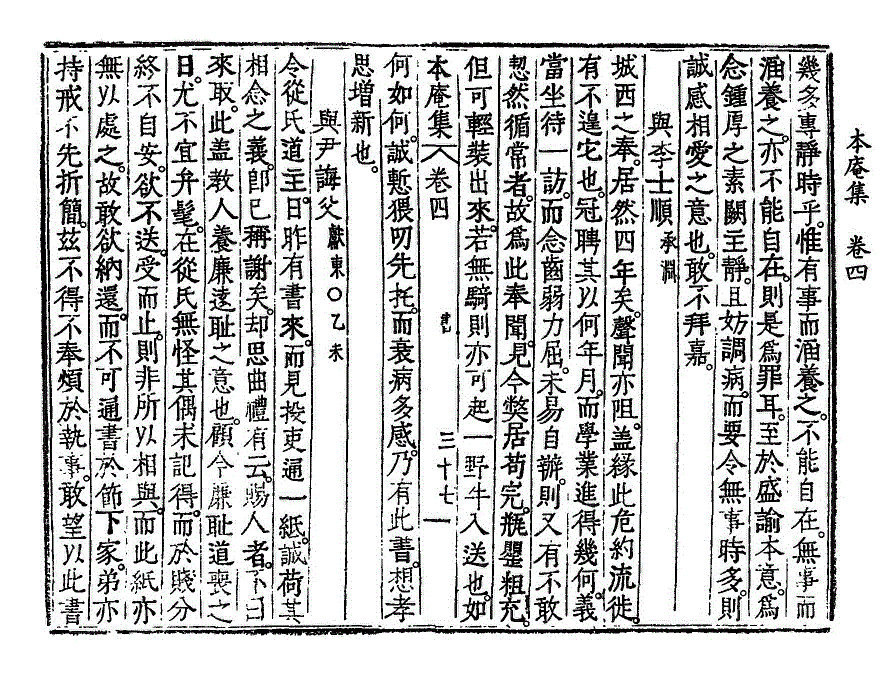 几多专静时乎。惟有事而涵养之。不能自在。无事而涵养之。亦不能自在。则是为罪耳。至于盛谕本意。为念钟厚之素阙主静。且妨调病。而要令无事时多。则诚感相爱之意也。敢不拜嘉。
几多专静时乎。惟有事而涵养之。不能自在。无事而涵养之。亦不能自在。则是为罪耳。至于盛谕本意。为念钟厚之素阙主静。且妨调病。而要令无事时多。则诚感相爱之意也。敢不拜嘉。与李士顺(承渊)
城西之奉。居然四年矣。声闻亦阻。盖缘此危约流徙。有不遑它也。冠聘其以何年月。而学业进得几何。义当坐待一访。而念齿弱力屈。未易自办。则又有不敢恝然循常者。故为此奉闻。见今弊居苟完。瓶罂粗充。但可轻装出来。若无骑则亦可起一野牛入送也。如何如何。诚惭猥叨先托。而衰病多感。乃有此书。想孝思增新也。
与尹诲父(献东○乙未)
令从氏道主。日昨有书来。而见投吏通一纸。诚荷其相念之义。即已称谢矣。却思曲礼有云。赐人者。不曰来取。此盖教人养廉远耻之意也。顾今廉耻道丧之日。尤不宜弁髦。在从氏无怪其偶未记得。而于贱分终不自安。欲不送。受而止。则非所以相与。而此纸亦无以处之。故敢欲纳还。而不可通书于节下家。弟亦持戒不先折简。玆不得不奉烦于执事。敢望以此书
本庵集卷四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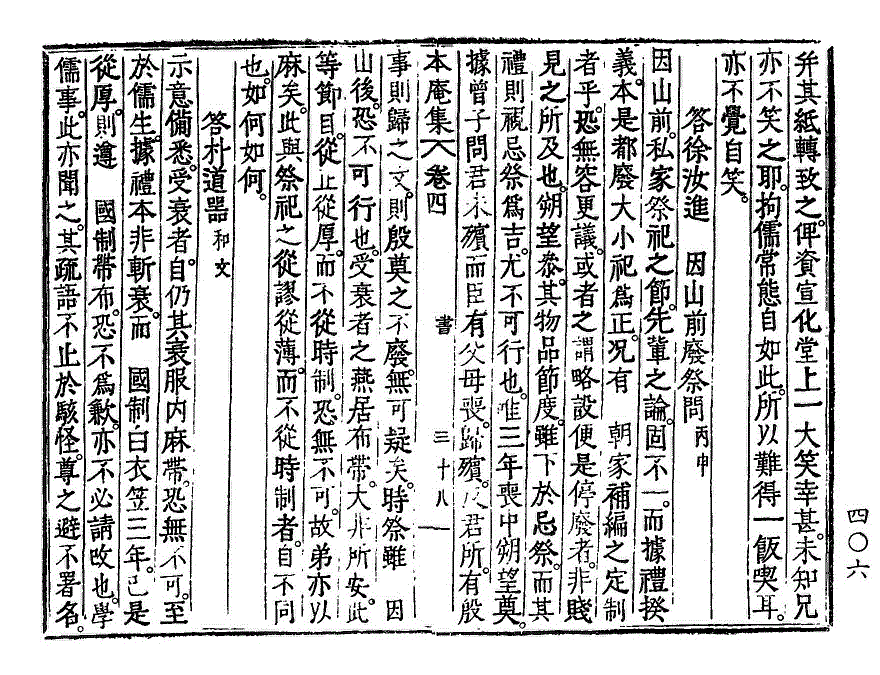 并其纸转致之。俾资宣化堂上一大笑幸甚。未知兄亦不笑之耶。拘儒常态自如此。所以难得一饭吃耳。亦不觉自笑。
并其纸转致之。俾资宣化堂上一大笑幸甚。未知兄亦不笑之耶。拘儒常态自如此。所以难得一饭吃耳。亦不觉自笑。答徐汝进 因山前废祭问(丙申)
因山前。私家祭祀之节。先辈之论。固不一。而据礼揆义。本是都废大小祀为正。况有 朝家补编之定制者乎。恐无容更议。或者之谓略设便是停废者。非贱见之所及也。朔望参。其物品节度。虽下于忌祭。而其礼则视忌祭为吉。尤不可行也。唯三年丧中朔望奠。据曾子问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丧。归殡。反君所。有殷事则归之文。则殷奠之不废。无可疑矣。时祭虽 因山后。恐不可行也。受衰者之燕居布带。大非所安。此等节目。从正从厚。而不从时制。恐无不可。故弟亦以麻矣。此与祭祀之从谬从薄。而不从时制者。自不同也。如何如何。
答朴道器(和文)
示意备悉。受衰者。自仍其衰服内麻带。恐无不可。至于儒生。据礼本非斩衰。而 国制白衣笠三年。已是从厚。则遵 国制带布。恐不为歉。亦不必请改也。学儒事。此亦闻之。其疏语不止于骇怪。尊之避不署名。
本庵集卷四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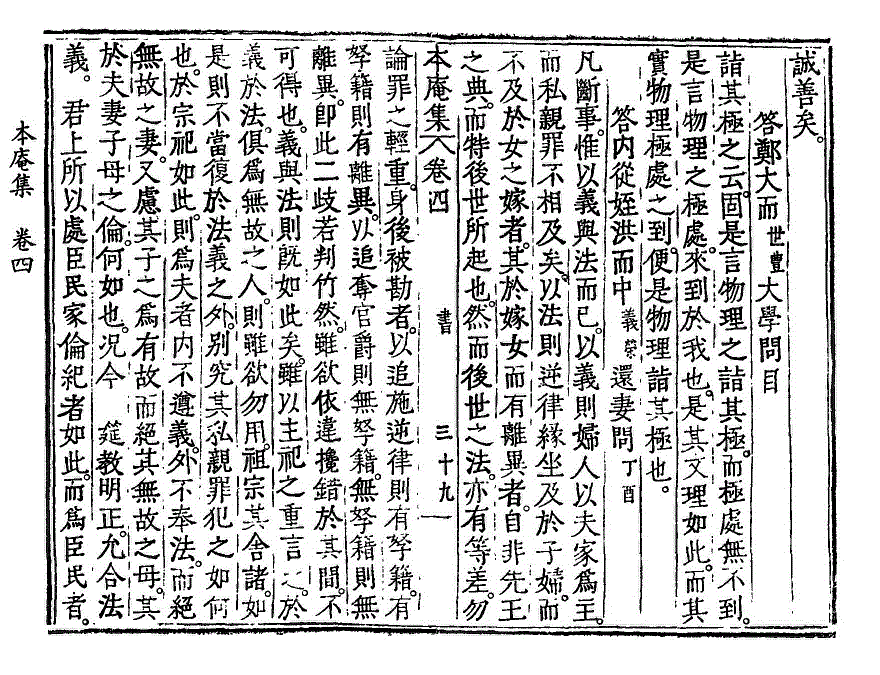 诚善矣。
诚善矣。答郑大而(世礼)大学问目
诣其极之云。固是言物理之诣其极。而极处无不到。是言物理之极处。来到于我也。是其文理如此。而其实物理极处之到。便是物理诣其极也。
答内从侄洪而中(义荣)还妻问(丁酉)
凡断事。惟以义与法而已。以义则妇人以夫家为主。而私亲罪不相及矣。以法则逆律缘坐及于子妇。而不及于女之嫁者。其于嫁女而有离异者。自非先王之典。而特后世所起也。然而后世之法。亦有等差。勿论罪之轻重。身后被勘者。以追施逆律则有孥籍。有孥籍则有离异。以追夺官爵则无孥籍。无孥籍则无离异。即此二歧若判竹然。虽欲依违搀错于其间。不可得也。义与法则既如此矣。虽以主祀之重言之。于义于法。俱为无故之人。则虽欲勿用。祖宗其舍诸。如是则不当复于法义之外。别究其私亲罪犯之如何也。于宗祀如此。则为夫者内不遵义。外不奉法。而绝无故之妻。又虑其子之为有故而绝其无故之母。其于夫妻子母之伦。何如也。况今 筵教明正。允合法义。 君上所以处臣民家伦纪者如此。而为臣民者。
本庵集卷四 第 4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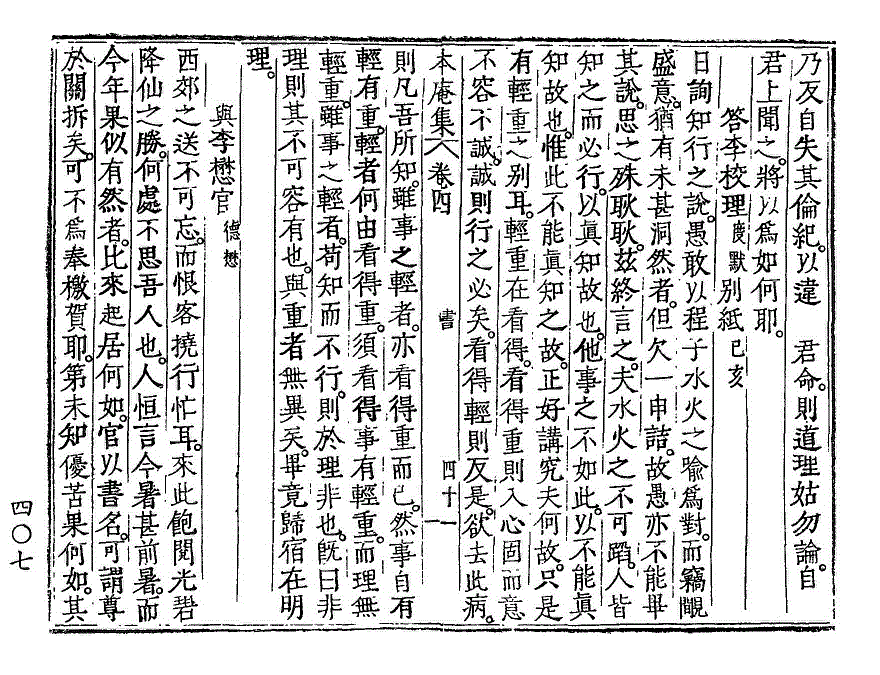 乃反自失其伦纪。以违 君命。则道理姑勿论。自 君上闻之。将以为如何耶。
乃反自失其伦纪。以违 君命。则道理姑勿论。自 君上闻之。将以为如何耶。答李校理(度默)别纸(己亥)
日询知行之说。愚敢以程子水火之喻为对。而窃覸盛意。犹有未甚洞然者。但欠一申诘。故愚亦不能毕其说。思之殊耿耿。玆终言之。夫水火之不可蹈。人皆知之而必行。以真知故也。他事之不如此。以不能真知故也。惟此不能真知之故。正好讲究夫何故。只是有轻重之别耳。轻重在看得。看得重则入心固而意不容不诚。诚则行之必矣。看得轻则反是。欲去此病。则凡吾所知。虽事之轻者。亦看得重而已。然事自有轻有重。轻者何由看得重。须看得事有轻重。而理无轻重。虽事之轻者。苟知而不行。则于理非也。既曰非理则其不可容有也。与重者无异矣。毕竟归宿在明理。
与李懋官(德懋)
西郊之送不可忘。而恨客挠行忙耳。来此饱阅光碧降仙之胜。何处不思吾人也。人恒言今暑甚前暑。而今年果似有然者。比来起居何如。官以书名。可谓尊于关拆矣。可不为奉檄贺耶。第未知优苦果何如。其
本庵集卷四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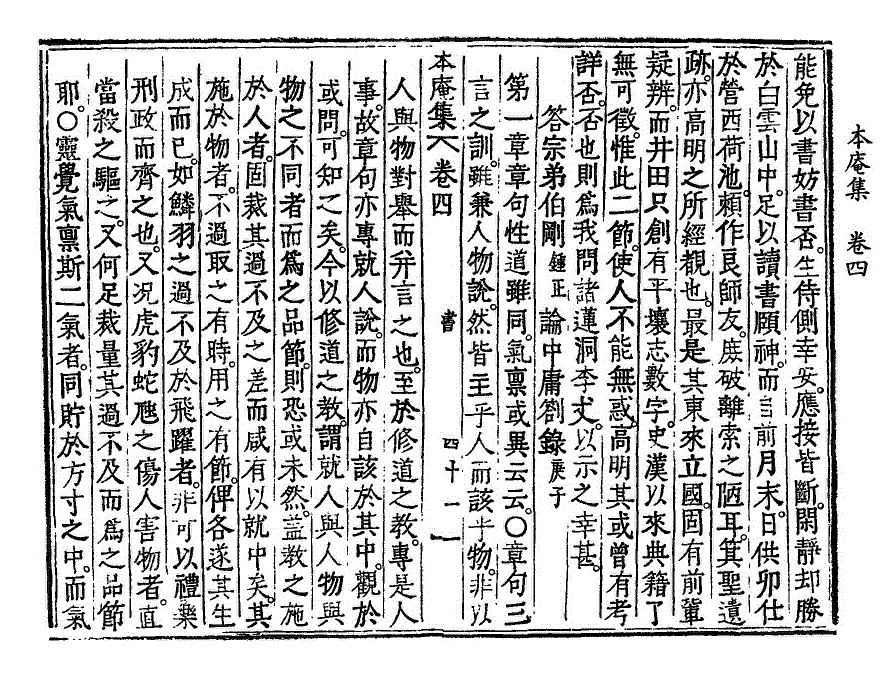 能免以书妨书否。生侍侧幸安。应接皆断。闲静却胜于白云山中。足以读书颐神。而自前月末。日供卯仕于营西荷池。赖作良师友。庶破离索之陋耳。箕圣遗迹。亦高明之所经睹也。最是其东来立国。固有前辈疑辨。而井田只创有平壤志数字。史汉以来典籍了无可徵。惟此二节。使人不能无惑。高明其或曾有考详否。否也则为我问诸莲洞李丈。以示之幸甚。
能免以书妨书否。生侍侧幸安。应接皆断。闲静却胜于白云山中。足以读书颐神。而自前月末。日供卯仕于营西荷池。赖作良师友。庶破离索之陋耳。箕圣遗迹。亦高明之所经睹也。最是其东来立国。固有前辈疑辨。而井田只创有平壤志数字。史汉以来典籍了无可徵。惟此二节。使人不能无惑。高明其或曾有考详否。否也则为我问诸莲洞李丈。以示之幸甚。答宗弟伯刚(钟正)论中庸劄录(庚子)
第一章章句性道虽同。气禀或异云云。○章句三言之训。虽兼人物说。然皆主乎人而该乎物。非以人与物对举而并言之也。至于修道之教。专是人事。故章句亦专就人说。而物亦自该于其中。观于或问。可知之矣。今以修道之教。谓就人与人物与物之不同者而为之品节。则恐或未然。盖教之施于人者。固裁其过不及之差而咸有以就中矣。其施于物者。不过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俾各遂其生成而已。如鳞羽之过不及于飞跃者。非可以礼乐刑政而齐之也。又况虎豹蛇虺之伤人害物者。直当杀之驱之。又何足裁量其过不及而为之品节耶。○灵觉气禀斯二气者。同贮于方寸之中。而气
本庵集卷四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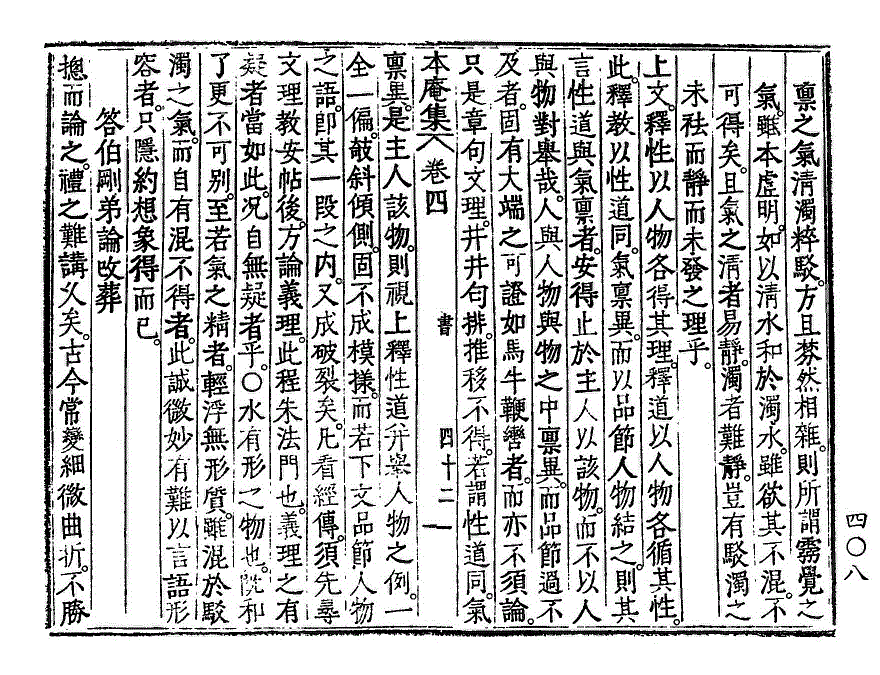 禀之气清浊粹驳。方且棼然相杂。则所谓灵觉之气。虽本虚明。如以清水和于浊水。虽欲其不混。不可得矣。且气之清者易静。浊者难静。岂有驳浊之未袪而静而未发之理乎。
禀之气清浊粹驳。方且棼然相杂。则所谓灵觉之气。虽本虚明。如以清水和于浊水。虽欲其不混。不可得矣。且气之清者易静。浊者难静。岂有驳浊之未袪而静而未发之理乎。上文。释性以人物各得其理。释道以人物各循其性。此释教以性道同。气禀异。而以品节人物结之。则其言性道与气禀者。安得止于主人以该物。而不以人与物对举哉。人与人物与物之中禀异。而品节过不及者。固有大端之可證如马牛鞭辔者。而亦不须论。只是章句文理。井井句排。推移不得。若谓性道同。气禀异。是主人该物。则视上释性道并举人物之例。一全一偏。攲斜倾侧。固不成模㨾。而若下文品节人物之语。即其一段之内。又成破裂矣。凡看经传。须先寻文理教安帖后。方论义理。此程朱法门也。义理之有疑者当如此。况自无疑者乎。○水有形之物也。既和了更不可别。至若气之精者。轻浮无形质。虽混于驳浊之气。而自有混不得者。此诚微妙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只隐约想象得而已。
答伯刚弟论改葬
总而论之。礼之难讲久矣。古今常变细微曲折。不胜
本庵集卷四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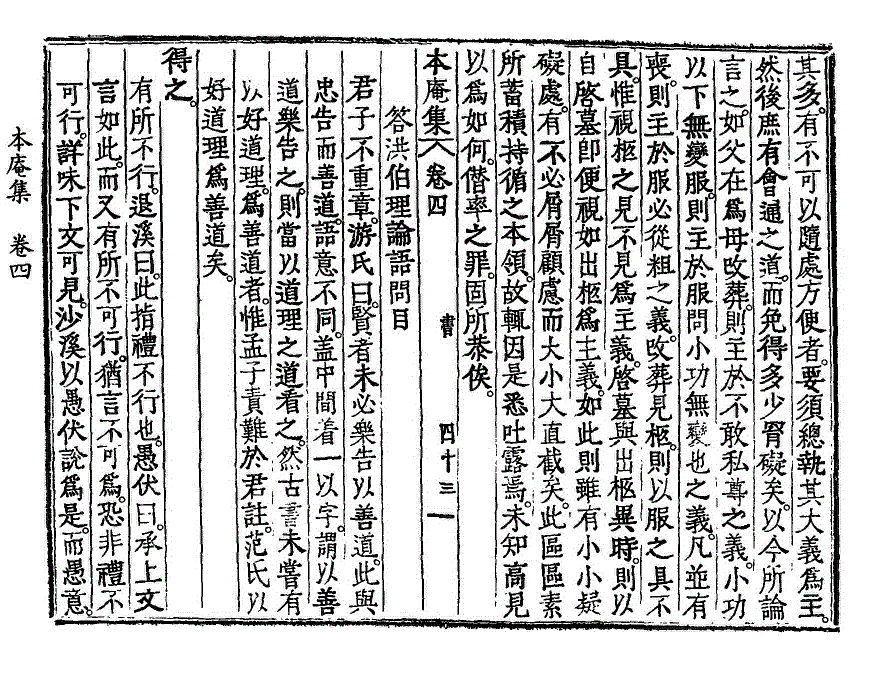 其多。有不可以随处方便者。要须总执其大义为主。然后庶有会通之道。而免得多少罥碍矣。以今所论言之。如父在为母改葬。则主于不敢私尊之义。小功以下无变服。则主于服问小功无变也之义。凡并有丧。则主于服必从粗之义。改葬见柩。则以服之具不具。惟视柩之见不见为主义。启墓与出柩异时。则以自启墓即便视如出柩为主义。如此则虽有小小疑碍处。有不必屑屑顾虑而大小大直截矣。此区区素所蓄积持循之本领。故辄因是悉吐露焉。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僭率之罪。固所恭俟。
其多。有不可以随处方便者。要须总执其大义为主。然后庶有会通之道。而免得多少罥碍矣。以今所论言之。如父在为母改葬。则主于不敢私尊之义。小功以下无变服。则主于服问小功无变也之义。凡并有丧。则主于服必从粗之义。改葬见柩。则以服之具不具。惟视柩之见不见为主义。启墓与出柩异时。则以自启墓即便视如出柩为主义。如此则虽有小小疑碍处。有不必屑屑顾虑而大小大直截矣。此区区素所蓄积持循之本领。故辄因是悉吐露焉。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僭率之罪。固所恭俟。答洪伯理论语问目
君子不重章。游氏曰。贤者未必乐告以善道。此与忠告而善道。语意不同。盖中间着一以字。谓以善道乐告之。则当以道理之道看之。然古书未尝有以好道理为善道者。惟孟子责难于君注。范氏以好道理为善道矣。
得之。
有所不行。退溪曰。此指礼不行也。愚伏曰。承上文言如此。而又有所不可行。犹言不可为。恐非礼不可行。详味下文可见。沙溪以愚伏说为是。而愚意
本庵集卷四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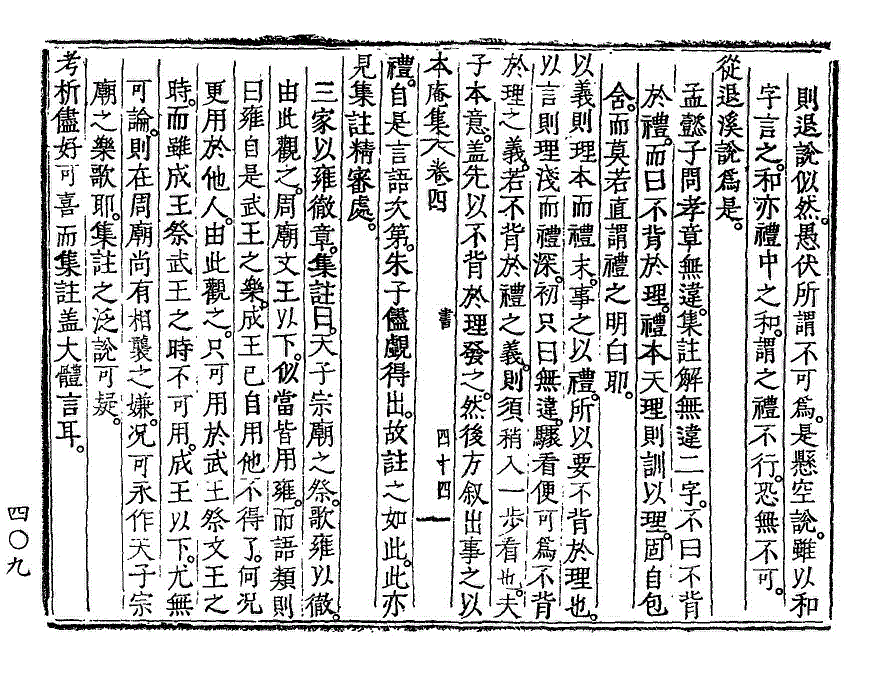 则退说似然。愚伏所谓不可为。是悬空说。虽以和字言之。和亦礼中之和。谓之礼不行。恐无不可。
则退说似然。愚伏所谓不可为。是悬空说。虽以和字言之。和亦礼中之和。谓之礼不行。恐无不可。从退溪说为是。
孟懿子问孝章无违。集注解无违二字。不曰不背于礼。而曰不背于理。礼本天理则训以理。固自包含。而莫若直谓礼之明白耶。
以义则理本而礼末。事之以礼。所以要不背于理也。以言则理浅而礼深。初只曰无违。骤看便可为不背于理之义。若不背于礼之义。则须稍入一步看也。夫子本意。盖先以不背于理发之。然后方叙出事之以礼。自是言语次第。朱子尽觑得出。故注之如此。此亦见集注精审处。
三家以雍彻章。集注曰。天子宗庙之祭。歌雍以彻。由此观之。周庙文王以下。似当皆用雍。而语类则曰雍自是武王之乐。成王已自用他不得了。何况更用于他人。由此观之。只可用于武王祭文王之时。而虽成王祭武王之时不可用。成王以下。尤无可论。则在周庙尚有相袭之嫌。况可永作天子宗庙之乐歌耶。集注之泛说可疑。
考析尽好可喜而集注盖大体言耳。
本庵集卷四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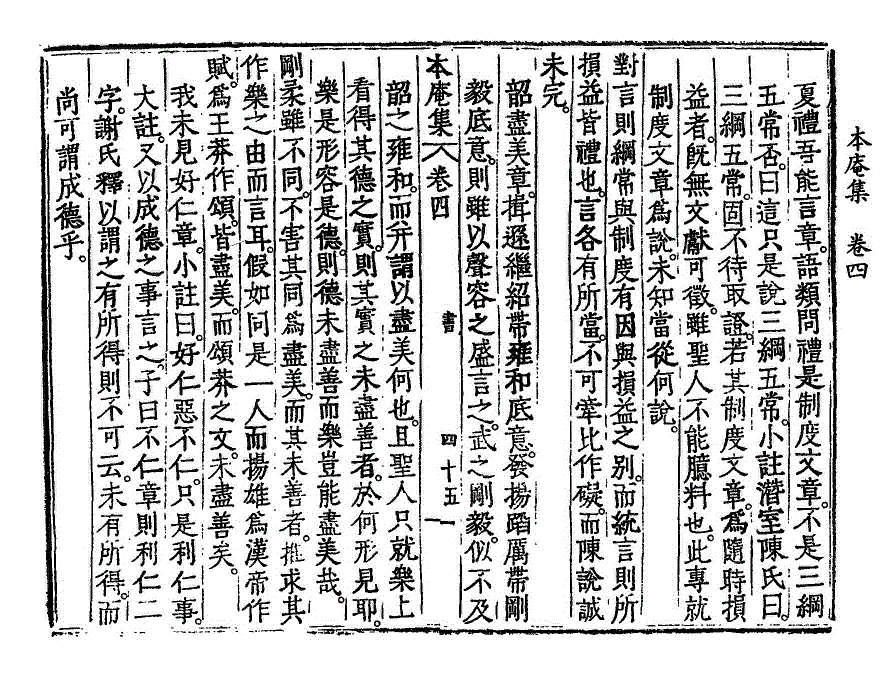 夏礼吾能言章。语类问礼是制度文章。不是三纲五常否。曰这只是说三纲五常。小注潜室陈氏曰。三纲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章。为随时损益者。既无文献可徵。虽圣人不能臆料也。此专就制度文章为说。未知当从何说。
夏礼吾能言章。语类问礼是制度文章。不是三纲五常否。曰这只是说三纲五常。小注潜室陈氏曰。三纲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章。为随时损益者。既无文献可徵。虽圣人不能臆料也。此专就制度文章为说。未知当从何说。对言则纲常与制度有因与损益之别。而统言则所损益皆礼也。言各有所当。不可牵比作碍。而陈说诚未完。
韶尽美章。揖逊继绍带雍和底意。发扬蹈厉带刚毅底意。则虽以声容之盛言之。武之刚毅。似不及韶之雍和。而并谓以尽美何也。且圣人只就乐上看得其德之实。则其实之未尽善者。于何形见耶。乐是形容是德。则德未尽善而乐岂能尽美哉。
刚柔虽不同。不害其同为尽美。而其未善者。推求其作乐之由而言耳。假如同是一人。而扬雄为汉帝作赋。为王莽作颂。皆尽美。而颂莽之文。未尽善矣。
我未见好仁章。小注曰。好仁恶不仁。只是利仁事。大注。又以成德之事言之。子曰不仁章则利仁二字。谢氏释以谓之有所得则不可云。未有所得。而尚可谓成德乎。
本庵集卷四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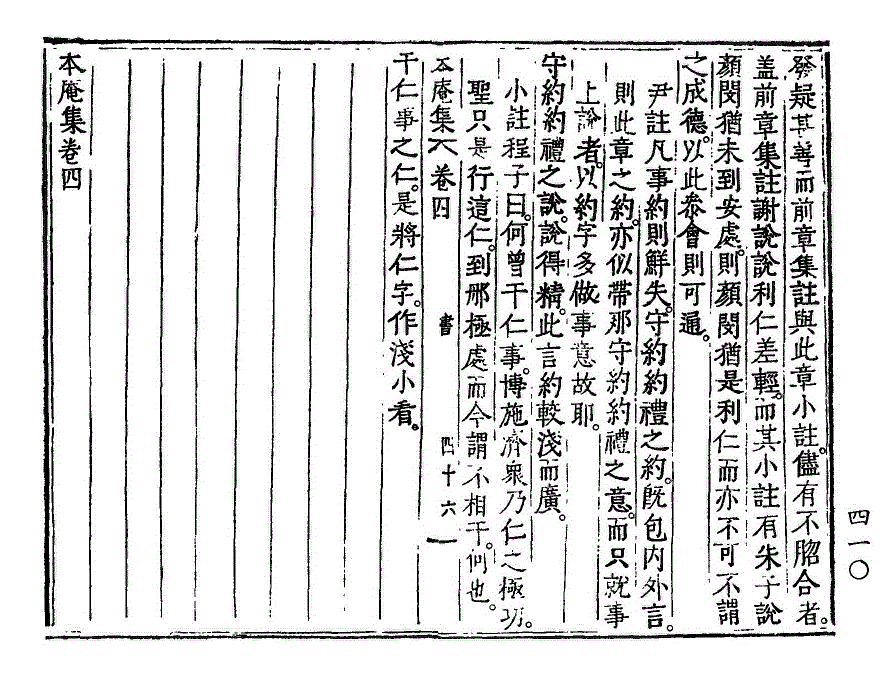 发疑甚善。而前章只注与此章小注。尽有不吻合者。盖前章集注谢说说利仁差轻。而其小注有朱子说颜闵犹未到安处。则颜闵犹是利仁而亦不可不谓之成德。以此参会则可通。
发疑甚善。而前章只注与此章小注。尽有不吻合者。盖前章集注谢说说利仁差轻。而其小注有朱子说颜闵犹未到安处。则颜闵犹是利仁而亦不可不谓之成德。以此参会则可通。尹注凡事约则鲜失。守约约礼之约。既包内外言。则此章之约。亦似带那守约约礼之意。而只就事上说者。以约字多做事意故耶。
守约约礼之说。说得精。此言约较浅而广。
小注程子曰。何曾干仁事。博施济众乃仁之极功。圣只是行这仁。到那极处而今谓不相干。何也。
干仁事之仁。是将仁字。作浅小看。
本庵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