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霅桥集卷四 第 x 页
霅桥集卷四
记
记
霅桥集卷四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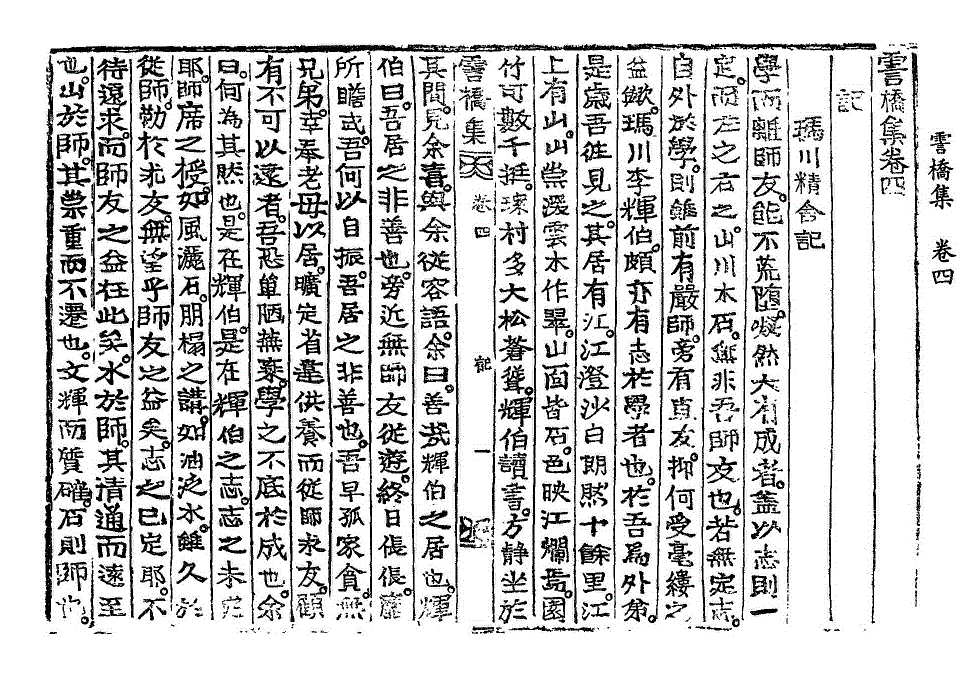 玛川精舍记
玛川精舍记学而离师友。能不荒堕。凝然大有成者。盖以志则一定。而左之右之。山川木石。无非吾师友也。若无定志。自外于学。则虽前有严师。旁有直友。抑何受毫缕之益欤。玛川李辉伯。颇亦有志于学者也。于吾为外弟。是岁吾往见之。其居有江。江澄沙白朗然十馀里。江上有山。山崇深云木作翠。山面皆石。色映江烂焉。园竹可数千挺。环村多大松苍耸。辉伯读书。方静坐于其间。见余喜。与余从容语。余曰。善哉辉伯之居也。辉伯曰。吾居之非善也。旁近无师友从游。终日伥伥。靡所瞻式。吾何以自振。吾居之非善也。吾早孤家贫。无兄弟。幸奉老母以居。旷定省违供养而从师求友。顾有不可以远者。吾恐单陋芜弃。学之不底于成也。余曰。何为其然也。是在辉伯。是在辉伯之志。志之未定耶。师席之授。如风洒石。朋榻之讲。如油泛水。虽久于从师。勤于求友。无望乎师友之益矣。志之已定耶。不待远求。而师友之益在此矣。水于师。其清通而远至也。山于师。其崇重而不迁也。文辉而质确。石则师也。
霅桥集卷四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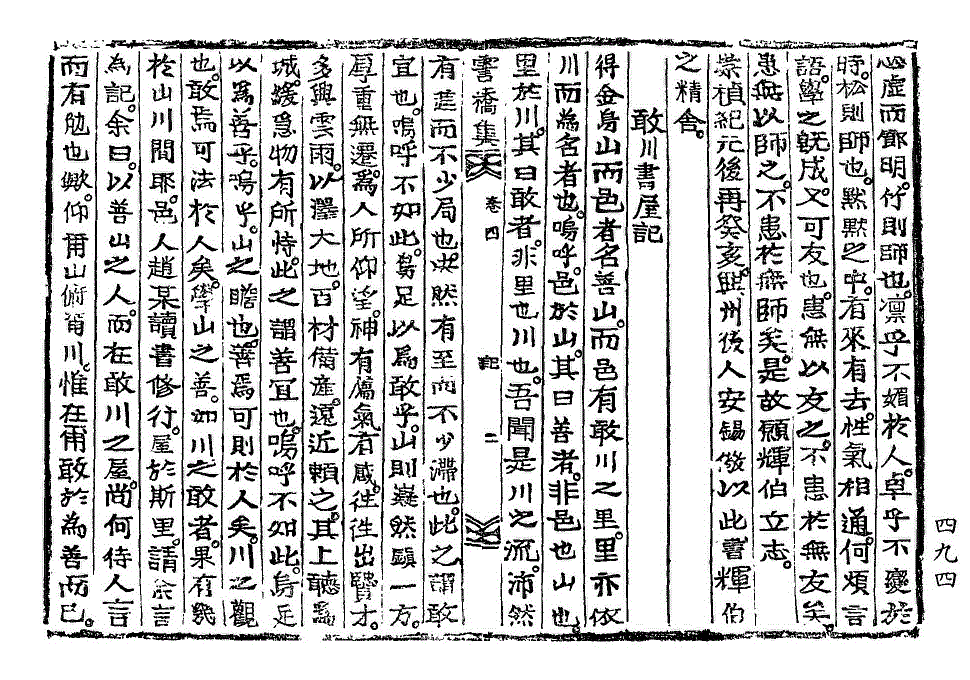 心虚而节明。竹则师也。凛乎不媚于人。卓乎不变于时。松则师也。默默之中。有来有去。性气相通。何烦言语。学之既成。又可友也。患无以友之。不患于无友矣。患无以师之。不患于无师矣。是故愿辉伯立志。崇祯纪元后再癸亥。兴州后人安锡儆以此书辉伯之精舍。
心虚而节明。竹则师也。凛乎不媚于人。卓乎不变于时。松则师也。默默之中。有来有去。性气相通。何烦言语。学之既成。又可友也。患无以友之。不患于无友矣。患无以师之。不患于无师矣。是故愿辉伯立志。崇祯纪元后再癸亥。兴州后人安锡儆以此书辉伯之精舍。敢川书屋记
得金乌山而邑者名善山。而邑有敢川之里。里亦依川而为名者也。呜呼。邑于山。其曰善者。非邑也山也。里于川。其曰敢者。非里也川也。吾闻是川之流。沛然有进而不少局也。决然有至而不少滞也。此之谓敢宜也。呜呼不如此。乌足以为敢乎。山则嶷然镇一方。厚重无迁。为人所仰望。神有属气有感。往往出贤才。多兴云雨。以泽大地。百材备产。远近赖之。其上听为城。缓急物有所恃。此之谓善宜也。呜呼不如此。乌足以为善乎。呜乎。山之瞻也。善焉可则于人矣。川之观也。敢焉可法于人矣。学山之善。如川之敢者。果有几于山川间耶。邑人赵某读书修行。屋于斯里。请余言为记。余曰。以善山之人。而在敢川之屋。尚何待人言而有勉也欤。仰尔山俯尔川。惟在尔敢于为善而已。
霅桥集卷四 第 495H 页
 讷斋记
讷斋记曩吾记权实甫默斋矣。实甫有弟曰阳仲。又以其斋名讷者求吾记。吾曰。子之兄弟。其亦有异乎人哉。世之人。兄多喧怒。弟多嚣怨。常理废绝。乖气横放。岂以弟之怨嚣。而兄则怒喧耶。抑以兄之怒喧。而弟则怨嚣耶。初必一是。末乃两非。呜呼良可悲也。今子之默与讷。视于彼者。亦大不同矣。顾未知兄默而弟随讷耶。抑弟讷而兄随默耶。且其已默已讷耶。抑亦欲默而欲讷耶。吾将见子一家中之常道流行。协气洋溢。独能复淳古之隆矣。传盖有之云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肰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乎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然而不兴者。未之有也。夫怀利以相接也。何由能默而能呐。怀仁义以相接也。亦何由喧怒而嚣怨。然则不喧怒而默。不嚣怨而呐。乃去利怀仁义者之为乎。家之兴可待。而实甫年长。盖已知此者。故此语于阳仲少者之斋。乃始悉之焉。
拟修皇明北伐檄文记
呜乎。自三代以降。开国之正。惟汉与皇明。而秦之秽虐。尚非纯戎狄。戎狄之丑。掩阳明据华夏。莫如元虏
霅桥集卷四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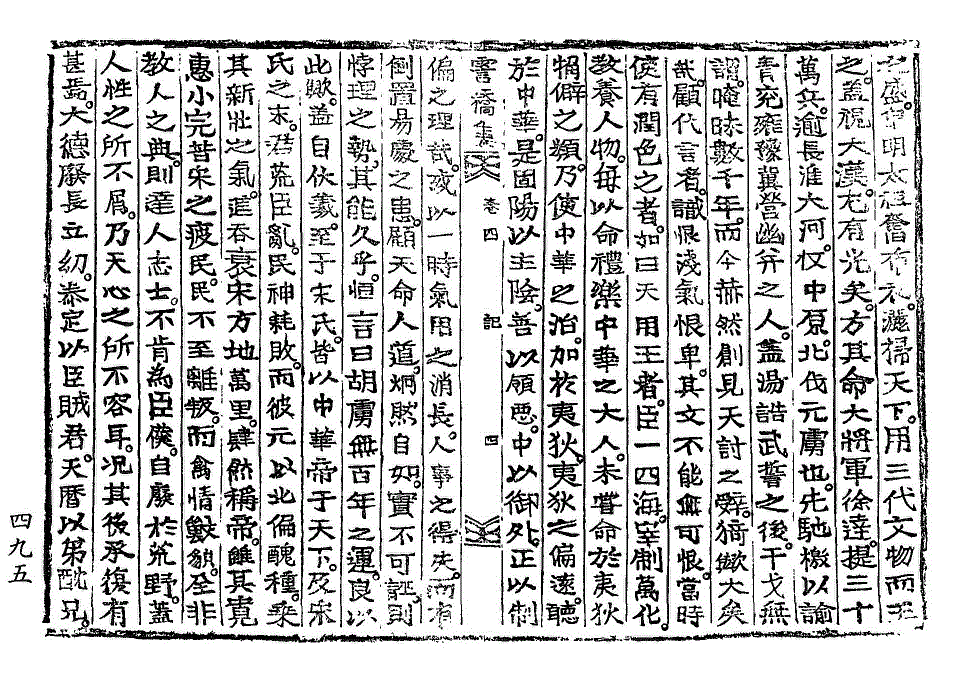 之盛。皇明太祖奋布衣。洒扫天下。用三代文物而王之。盖视大汉。尤有光矣。方其命大将军徐达。提三十万兵。逾长淮大河。收中原。北伐元虏也。先驰檄以谕青兖雍豫冀营幽并之人。盖汤诰武誓之后。干戈无谓。晻昧数千年。而今赫然创见天讨之辞。猗欤大矣哉。顾代言者。识恨浅气恨卑。其文不能无可恨。当时使有润色之者。如曰天用王者。臣一四海。宰制万化。教养人物。每以命礼乐中华之大人。未尝命于夷狄觕僻之类。乃使中华之治。加于夷狄。夷狄之偏远。听于中华。是固阳以主阴。善以领恶。中以御外。正以制偏之理哉。或以一时气用之消长。人事之得失。而有倒置易处之患。愿天命人道。炯然自如。实不可诬。则悖理之势。其能久乎。恒言曰胡虏无百年之运。良以此欤。盖自伏羲。至于宋氏。皆以中华帝于天下。及宋氏之末。君荒臣乱。民神耗败。而彼元以北偏丑种。乘其新壮之气。进吞衰宋方地万里。肆然称帝。虽其宽惠小完苦宋之疲民。民不至离叛。而禽情兽貌。全非教人之典。则达人志士。不肯为臣仆。自废于荒野。盖人性之所不屑。乃天心之所不容耳。况其后承复有甚焉。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贼君。天历以弟酖兄。
之盛。皇明太祖奋布衣。洒扫天下。用三代文物而王之。盖视大汉。尤有光矣。方其命大将军徐达。提三十万兵。逾长淮大河。收中原。北伐元虏也。先驰檄以谕青兖雍豫冀营幽并之人。盖汤诰武誓之后。干戈无谓。晻昧数千年。而今赫然创见天讨之辞。猗欤大矣哉。顾代言者。识恨浅气恨卑。其文不能无可恨。当时使有润色之者。如曰天用王者。臣一四海。宰制万化。教养人物。每以命礼乐中华之大人。未尝命于夷狄觕僻之类。乃使中华之治。加于夷狄。夷狄之偏远。听于中华。是固阳以主阴。善以领恶。中以御外。正以制偏之理哉。或以一时气用之消长。人事之得失。而有倒置易处之患。愿天命人道。炯然自如。实不可诬。则悖理之势。其能久乎。恒言曰胡虏无百年之运。良以此欤。盖自伏羲。至于宋氏。皆以中华帝于天下。及宋氏之末。君荒臣乱。民神耗败。而彼元以北偏丑种。乘其新壮之气。进吞衰宋方地万里。肆然称帝。虽其宽惠小完苦宋之疲民。民不至离叛。而禽情兽貌。全非教人之典。则达人志士。不肯为臣仆。自废于荒野。盖人性之所不屑。乃天心之所不容耳。况其后承复有甚焉。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贼君。天历以弟酖兄。霅桥集卷四 第 496H 页
 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已甚矣。人君者臣民之标准。朝廷者天下之根源。五典者王政之纲纪。彼乃颓其纲纪。失于标准。悖于根源如此。无非污染陷败斯人者。则岂独不可以教耶。及其末王。淫荒无度。加以宰相专杀。宪台报怨。百司毒虐。即并与其养人者而亡之。于是人心离散。九州兵起。使我中原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哀哉。盖其社稷甚危。虽因夷德荒败。其气乖敝而然。抑所谓天定胜人。而其道好还之时欤。神人之愤。积而始发。华夏之气。郁而方伸。丑虏之势。倾而将覆。当此之时。天必已眷中原。命其圣人。驱逐胡虏。恢复华夏。立纲陈纪。匡济神民。今一纪于玆。未闻有应天顺人者。而忍使尔等战战慄慄。处于朝秦暮楚之土。诚为矜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鸟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阻兵据险。互相吞噬。顾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胜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汉沔湖湘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
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已甚矣。人君者臣民之标准。朝廷者天下之根源。五典者王政之纲纪。彼乃颓其纲纪。失于标准。悖于根源如此。无非污染陷败斯人者。则岂独不可以教耶。及其末王。淫荒无度。加以宰相专杀。宪台报怨。百司毒虐。即并与其养人者而亡之。于是人心离散。九州兵起。使我中原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哀哉。盖其社稷甚危。虽因夷德荒败。其气乖敝而然。抑所谓天定胜人。而其道好还之时欤。神人之愤。积而始发。华夏之气。郁而方伸。丑虏之势。倾而将覆。当此之时。天必已眷中原。命其圣人。驱逐胡虏。恢复华夏。立纲陈纪。匡济神民。今一纪于玆。未闻有应天顺人者。而忍使尔等战战慄慄。处于朝秦暮楚之土。诚为矜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鸟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阻兵据险。互相吞噬。顾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胜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汉沔湖湘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霅桥集卷四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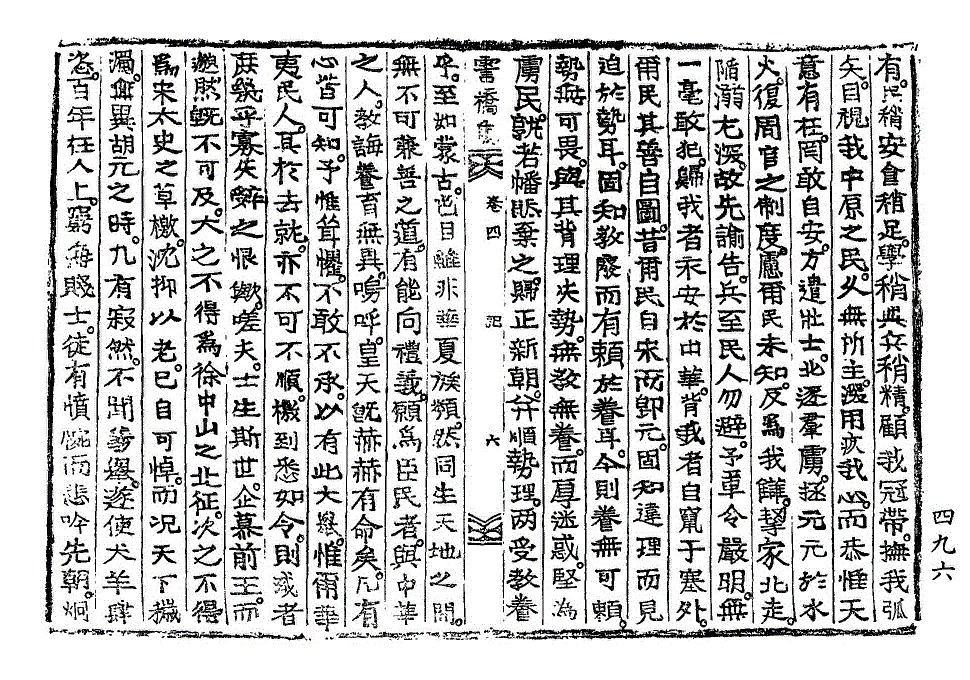 有。民稍安食稍足。学稍兴兵稍精。顾我冠带。抚我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我心。而恭惟天意有在。罔敢自安。方遣壮士。北逐群虏。拯元元于水火。复周官之制度。虑尔民未知。反为我雠。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军令严明。无一毫敢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尔民其善自图。昔尔民自宋而即元。固知违理而见迫于势耳。固知教废而有赖于养耳。今则养无可赖。势无可畏。与其背理失势。无教无养。而厚迷惑。坚为虏民。孰若幡然弃之。归正新朝。并顺势理。两受教养乎。至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无不可兼善之道。有能向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人。教诲养育无异。呜呼。皇天既赫赫有命矣。凡有心皆可知。予惟䇯惧。不敢不承。以有此大举。惟尔华夷民人。其于去就。亦不可不顺。檄到悉如令。则或者庶几乎寡失辞之恨欤。嗟夫。士生斯世。企慕前王。而邈然既不可及。大之不得为徐中山之北征。次之不得为宋太史之草檄。沈抑以老。已自可悼。而况天下秽浊。无异胡元之时。九有寂然。不闻义举。遂使犬羊肆恣。百年在人上。穷海贱士。徒有愤惋而悲吟先朝。炯
有。民稍安食稍足。学稍兴兵稍精。顾我冠带。抚我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我心。而恭惟天意有在。罔敢自安。方遣壮士。北逐群虏。拯元元于水火。复周官之制度。虑尔民未知。反为我雠。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军令严明。无一毫敢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尔民其善自图。昔尔民自宋而即元。固知违理而见迫于势耳。固知教废而有赖于养耳。今则养无可赖。势无可畏。与其背理失势。无教无养。而厚迷惑。坚为虏民。孰若幡然弃之。归正新朝。并顺势理。两受教养乎。至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无不可兼善之道。有能向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人。教诲养育无异。呜呼。皇天既赫赫有命矣。凡有心皆可知。予惟䇯惧。不敢不承。以有此大举。惟尔华夷民人。其于去就。亦不可不顺。檄到悉如令。则或者庶几乎寡失辞之恨欤。嗟夫。士生斯世。企慕前王。而邈然既不可及。大之不得为徐中山之北征。次之不得为宋太史之草檄。沈抑以老。已自可悼。而况天下秽浊。无异胡元之时。九有寂然。不闻义举。遂使犬羊肆恣。百年在人上。穷海贱士。徒有愤惋而悲吟先朝。炯霅桥集卷四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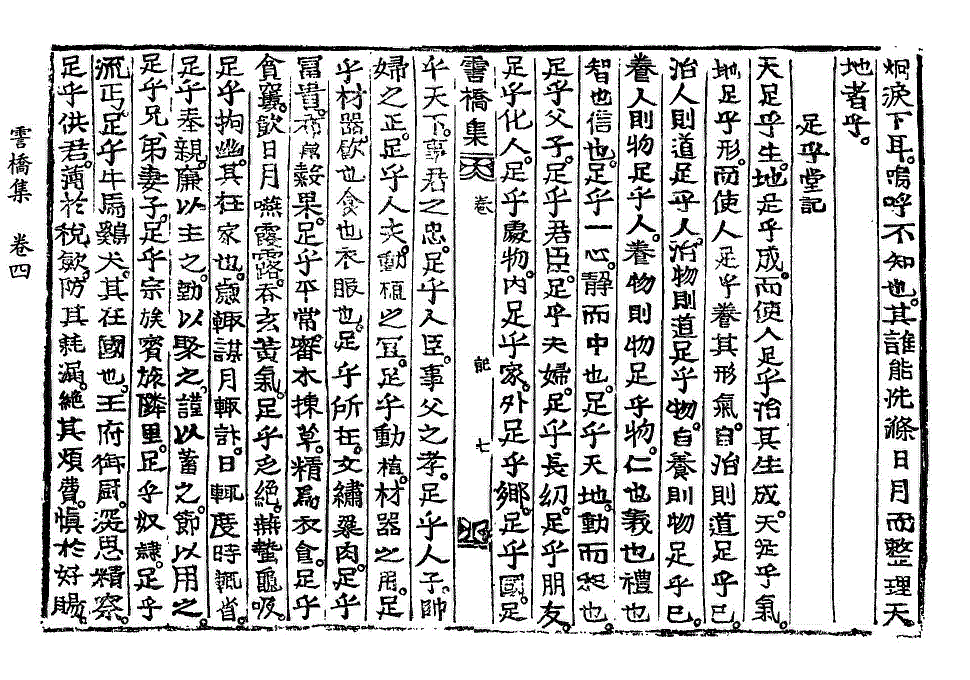 炯泪下耳。呜呼不知也。其谁能洗涤日月而整理天地者乎。
炯泪下耳。呜呼不知也。其谁能洗涤日月而整理天地者乎。足乎堂记
天足乎生。地足乎成。而使人足乎治其生成。天足乎气。地足乎形。而使人足乎养其形气。自治则道足乎己。治人则道足乎人。治物则道足乎物。自养则物足乎己。养人则物足乎人。养物则物足乎物。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足乎一心。静而中也。足乎天地。动而和也。足乎父子。足乎君臣。足乎夫妇。足乎长幼。足乎朋友。足乎化人。足乎处物。内足乎家。外足乎乡。足乎国。足乎天下。事君之忠。足乎人臣。事父之孝。足乎人子。帅妇之正。足乎人夫。动植之宜。足乎动植。材器之用。足乎材器。饮也食也衣服也。足乎所在。文绣粱肉。足乎富贵。布帛谷果。足乎平常。审木㨂草。精为衣食。足乎贫窭。饮日月咽霞露。吞玄黄气。足乎乏绝。燕蛰龟吸。足乎拘幽。其在家也。岁辄谋月辄计。日辄度时辄省。足乎奉亲。廉以主之。勤以聚之。谨以蓄之。节以用之。足乎兄弟妻子。足乎宗族宾旅邻里。足乎奴隶。足乎流丏。足乎牛马鸡犬。其在国也。王府御厨。深思精察。足乎供君。薄于税敛。防其耗漏。绝其烦费。慎于好赐。
霅桥集卷四 第 497L 页
 丰于常禄。足乎百官。足乎府史胥徒。因居而与之宅。因耕而与之钱。因蚕而为之节。因畜而为之制。山泽有禁而勿暴。关市有讥而勿厄。足乎商贾。足乎工虞。足乎农民。破除佛老。赡给学校。足乎正学之士。至于物也。遂其方长。损其太盛。顺其时和。畅其土润。足乎鸟兽虫鱼。足乎百谷草木。盖天之命于人以治生成养形气者。各足乎人人。初岂有一人不得足乎哉。顾众人徇物则失之。君子徇道则全之。呜呼可不慎欤。君子本于自治而及于治人治物。厚于养人养物而薄于自养。既足乎自治。而所本则立矣。宁患不足乎治人与物也欤。且求足乎养人与物。而所让者多矣。宁知不足乎自养也欤。众人急于治人治物而怠于自治。过于自养而忽于养人养物。既不足乎自治。而患无以推及矣。尚有可足乎治人与物者欤。且求过足乎自养。而患无以厌蒲矣。尚有可足乎养人与物者欤。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夫笃于自治而易足乎徇道。轻于自养而易足乎须物。此君子之所以无不足乎己而坦荡荡者也。略于自治而难足乎须道。滥于自养而难足乎徇物。此众人之所以每不足乎己而长戚戚者也。噫。君子之所求者。求天下
丰于常禄。足乎百官。足乎府史胥徒。因居而与之宅。因耕而与之钱。因蚕而为之节。因畜而为之制。山泽有禁而勿暴。关市有讥而勿厄。足乎商贾。足乎工虞。足乎农民。破除佛老。赡给学校。足乎正学之士。至于物也。遂其方长。损其太盛。顺其时和。畅其土润。足乎鸟兽虫鱼。足乎百谷草木。盖天之命于人以治生成养形气者。各足乎人人。初岂有一人不得足乎哉。顾众人徇物则失之。君子徇道则全之。呜呼可不慎欤。君子本于自治而及于治人治物。厚于养人养物而薄于自养。既足乎自治。而所本则立矣。宁患不足乎治人与物也欤。且求足乎养人与物。而所让者多矣。宁知不足乎自养也欤。众人急于治人治物而怠于自治。过于自养而忽于养人养物。既不足乎自治。而患无以推及矣。尚有可足乎治人与物者欤。且求过足乎自养。而患无以厌蒲矣。尚有可足乎养人与物者欤。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夫笃于自治而易足乎徇道。轻于自养而易足乎须物。此君子之所以无不足乎己而坦荡荡者也。略于自治而难足乎须道。滥于自养而难足乎徇物。此众人之所以每不足乎己而长戚戚者也。噫。君子之所求者。求天下霅桥集卷四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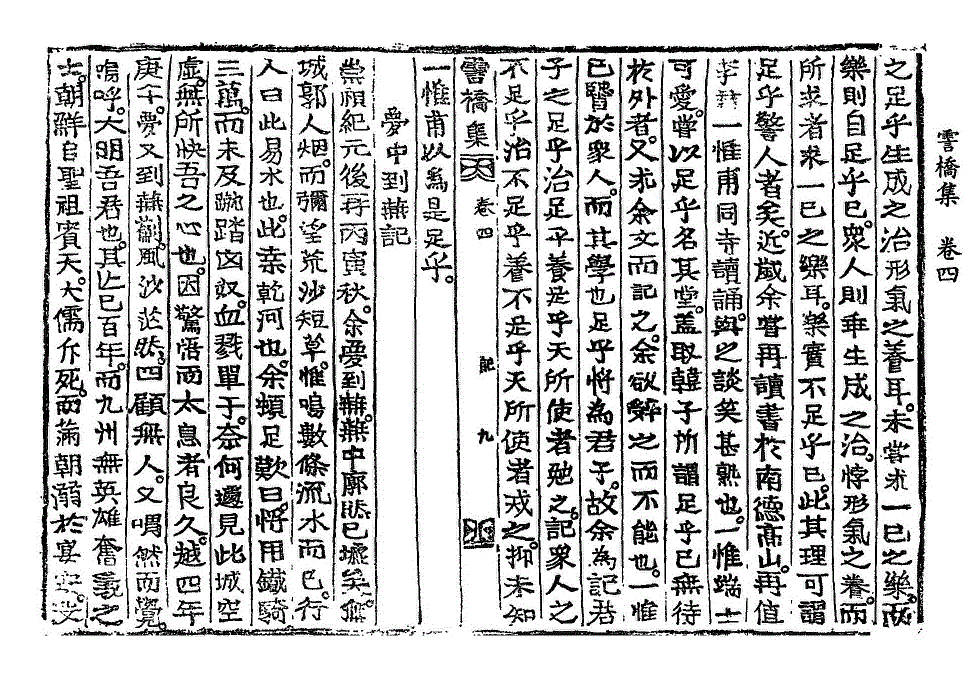 之足乎生成之治形气之养耳。未尝求一己之乐。而乐则自足乎己。众人则乖生成之治。悖形气之养。而所求者求一己之乐耳。乐实不足乎己。此其理可谓足乎警人者矣。近岁余尝再读书于南德高山。再值李君一惟甫同寺读诵。与之谈笑甚熟也。一惟端士可爱。尝以足乎名其堂。盖取韩子所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又求余文而记之。余欲辞之而不能也。一惟已贤于众人。而其学也足乎将为君子。故余为记君子之足乎治足乎养足乎天所使者勉之。记众人之不足乎治不足乎养不足乎天所使者戒之。抑未知一惟甫以为是足乎。
之足乎生成之治形气之养耳。未尝求一己之乐。而乐则自足乎己。众人则乖生成之治。悖形气之养。而所求者求一己之乐耳。乐实不足乎己。此其理可谓足乎警人者矣。近岁余尝再读书于南德高山。再值李君一惟甫同寺读诵。与之谈笑甚熟也。一惟端士可爱。尝以足乎名其堂。盖取韩子所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又求余文而记之。余欲辞之而不能也。一惟已贤于众人。而其学也足乎将为君子。故余为记君子之足乎治足乎养足乎天所使者勉之。记众人之不足乎治不足乎养不足乎天所使者戒之。抑未知一惟甫以为是足乎。梦中到燕记
崇祯纪元后再丙寅秋。余梦到燕。燕中廓然已墟矣。无城郭人烟。而弥望荒沙短草。惟鸣数条流水而已。行人曰此易水也。此桑乾河也。余顿足叹曰。将用铁骑三万。而未及蹴踏凶奴。血戮单于。奈何遽见此城空虚。无所快吾之心也。因惊悟而太息者良久。越四年庚午。梦又到燕蓟。风沙茫然。四顾无人。又喟然而觉。呜呼。大明吾君也。其亡已百年。而九州无英雄奋义之士。朝鲜自圣祖宾天。大儒斥死。而满朝溺于宴安。没
霅桥集卷四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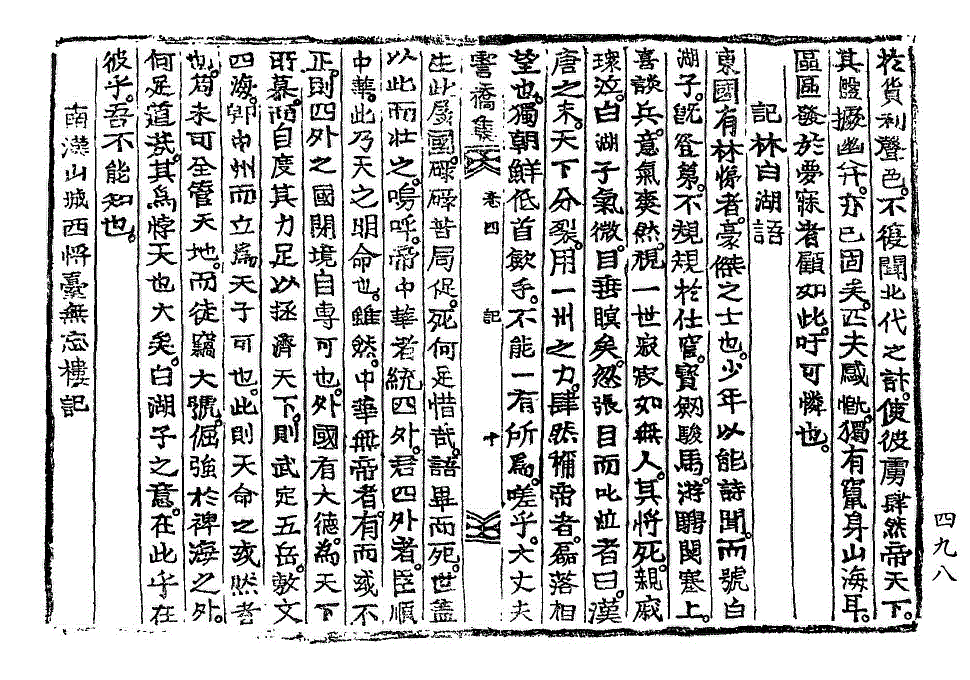 于货利声色。不复闻北代(一作伐)之计。使彼虏肆然帝天下。其盘据幽并。亦已固矣。匹夫感慨。独有窜身山海耳。区区发于梦寐者顾如此。吁可怜也。
于货利声色。不复闻北代(一作伐)之计。使彼虏肆然帝天下。其盘据幽并。亦已固矣。匹夫感慨。独有窜身山海耳。区区发于梦寐者顾如此。吁可怜也。记林白湖语
东国有林悌者。豪杰之士也。少年以能诗闻。而号白湖子。既登第。不规规于仕宦。宝剑骏马。游骋关塞上。喜谈兵。意气爽然。视一世寂寂如无人。其将死。亲戚环泣。白湖子气微。目垂瞑矣。忽张目而叱泣者曰。汉唐之末。天下分裂。用一州之力。肆然称帝者。磊落相望也。独朝鲜低首敛手。不能一有所为。嗟乎。大丈夫生此孱国。碌碌苦局促。死何足惜哉。语毕而死。世盖以此而壮之。呜呼。帝中华者统四外。君四外者。臣顺中华。此乃天之明命也。虽然。中华无帝者。有而或不正。则四外之国闭境自专可也。外国有大德。为天下所慕。而自度其力足以拯济天下。则武定五岳。敷文四海。即中州而立为天子可也。此则天命之或然者也。苟未可全管天地。而徒窃大号。倔强于裨海之外。何足道哉。其为悖天也大矣。白湖子之意。在此乎在彼乎。吾不能知也。
南汉山城西将台无忘楼记
霅桥集卷四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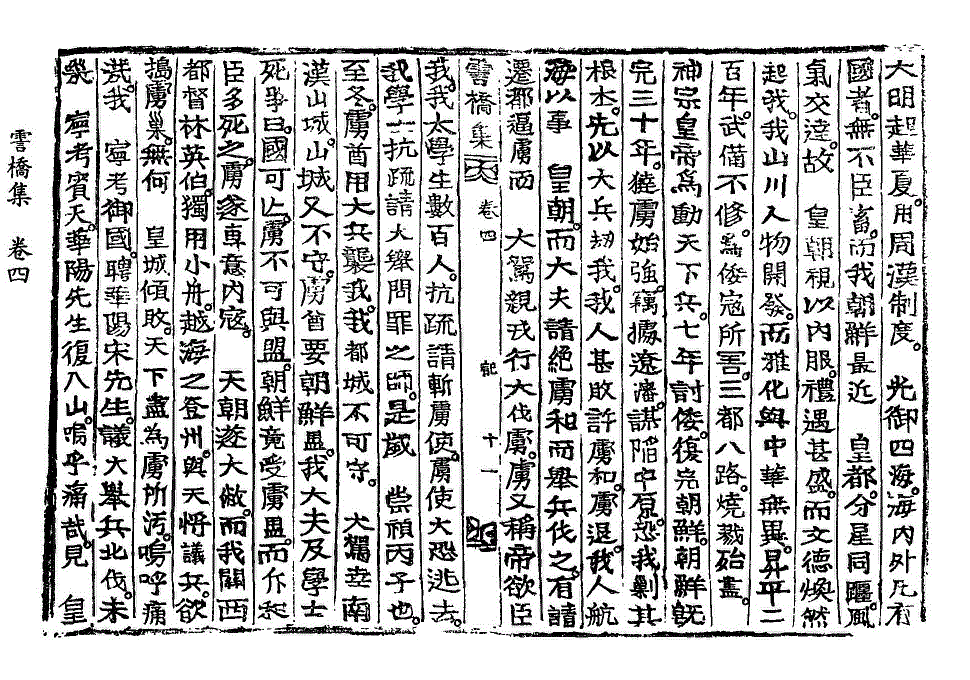 大明起华夏。用周汉制度。 光御四海。海内外凡有国者。无不臣畜。而我朝鲜最近 皇都。分星同躔。风气交达。故 皇朝视以内服。礼遇甚盛。而文德焕然起我。我山川人物开发。而雅化与中华无异。升平二百年。武备不修。为倭寇所害。三都八路。烧戮殆尽。 神宗皇帝为动天下兵。七年讨倭。复完朝鲜。朝鲜既完三十年。獭虏始强。窃据辽沈。谋陷中原。恐我剿其根本。先以大兵劫我。我人甚败许虏和。虏退。我人航海以事 皇朝。而大夫请绝虏和而举兵伐之。有请迁都逼虏而 大驾亲戎行大伐虏。虏又称帝欲臣我。我太学生数百人。抗疏请斩虏使。虏使大恐逃去。我学士抗疏请大举问罪之师。是岁 崇祯丙子也。至冬。虏酋用大兵袭我。我都城不可守。 大驾幸南汉山城。山城又不守。虏酋要朝鲜盟。我大夫及学士死争曰。国可亡。虏不可与盟。朝鲜竟受虏盟。而斥和臣多死之。虏遂专意内寇。 天朝遂大敝。而我关西都督林英伯。独用小舟。越海之登州。与天将议兵。欲捣虏巢。无何 皇城倾败。天下尽为虏所污。呜呼痛哉。我 宁考御国。聘华阳宋先生。议大举兵北伐。未几 宁考宾天。华阳先生复入山。呜乎痛哉。见 皇
大明起华夏。用周汉制度。 光御四海。海内外凡有国者。无不臣畜。而我朝鲜最近 皇都。分星同躔。风气交达。故 皇朝视以内服。礼遇甚盛。而文德焕然起我。我山川人物开发。而雅化与中华无异。升平二百年。武备不修。为倭寇所害。三都八路。烧戮殆尽。 神宗皇帝为动天下兵。七年讨倭。复完朝鲜。朝鲜既完三十年。獭虏始强。窃据辽沈。谋陷中原。恐我剿其根本。先以大兵劫我。我人甚败许虏和。虏退。我人航海以事 皇朝。而大夫请绝虏和而举兵伐之。有请迁都逼虏而 大驾亲戎行大伐虏。虏又称帝欲臣我。我太学生数百人。抗疏请斩虏使。虏使大恐逃去。我学士抗疏请大举问罪之师。是岁 崇祯丙子也。至冬。虏酋用大兵袭我。我都城不可守。 大驾幸南汉山城。山城又不守。虏酋要朝鲜盟。我大夫及学士死争曰。国可亡。虏不可与盟。朝鲜竟受虏盟。而斥和臣多死之。虏遂专意内寇。 天朝遂大敝。而我关西都督林英伯。独用小舟。越海之登州。与天将议兵。欲捣虏巢。无何 皇城倾败。天下尽为虏所污。呜呼痛哉。我 宁考御国。聘华阳宋先生。议大举兵北伐。未几 宁考宾天。华阳先生复入山。呜乎痛哉。见 皇霅桥集卷四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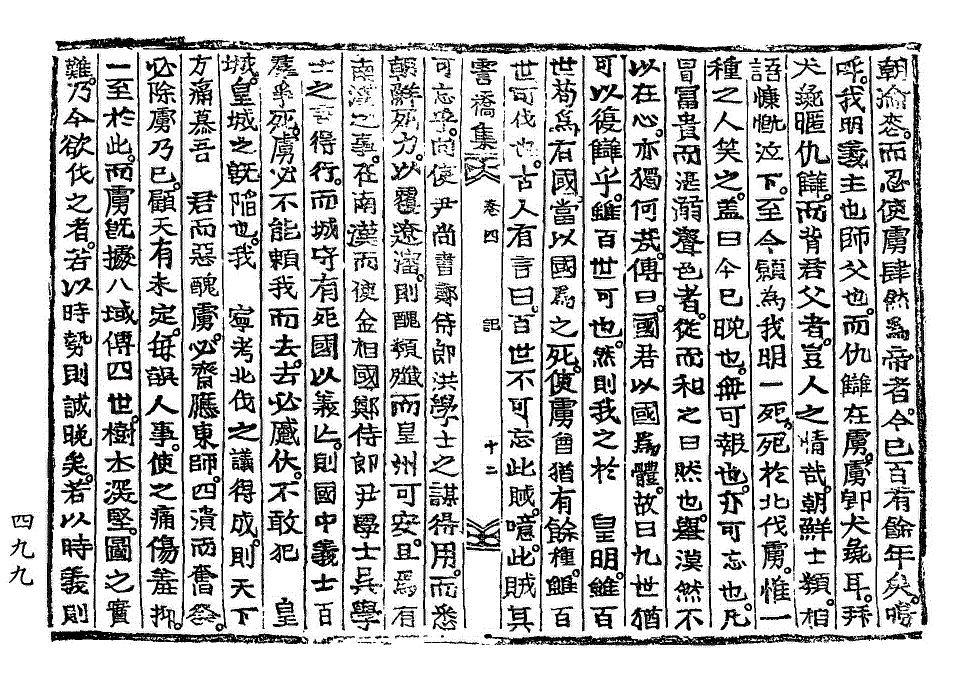 朝沦丧。而忍使虏肆然为帝者。今已百有馀年矣。呜呼。我明义主也师父也。而仇雠在虏。虏即犬彘耳。拜犬彘昵仇雠。而背君父者。岂人之情哉。朝鲜士类。相语慷慨泣下。至今愿为我明一死。死于北伐虏。惟一种之人笑之。盖曰今已晚也。无可报也。亦可忘也。凡冒富贵而湛溺声色者。从而和之曰然也。举漠然不以在心。亦独何哉。传曰。国君以国为体。故曰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然则我之于 皇明。虽百世苟为有国。当以国为之死。使虏酋犹有馀种。虽百世可伐也。古人有言曰。百世不可忘此贼。噫。此贼其可忘乎。向使尹尚书郑侍郎洪学士之谋得用。而悉朝鲜死力。以覆辽沈。则丑类歼而皇州可安。且焉有南汉之事。在南汉而使金相国郑侍郎尹学士吴学士之言得行。而城守有死国以义亡。则国中义士百群争死。虏必不能赖我而去。去必蹙伏。不敢犯 皇城。皇城之既陷也。我 宁考北伐之议得成。则天下方痛慕吾 君而恶丑虏。必斋应东师。四溃而奋发。必除虏乃已。顾天有未定。每误人事。使之痛伤羞抑。一至于此。而虏既据八域传四世。树本深坚。图之实难。乃今欲伐之者。若以时势则诚晚矣。若以时义则
朝沦丧。而忍使虏肆然为帝者。今已百有馀年矣。呜呼。我明义主也师父也。而仇雠在虏。虏即犬彘耳。拜犬彘昵仇雠。而背君父者。岂人之情哉。朝鲜士类。相语慷慨泣下。至今愿为我明一死。死于北伐虏。惟一种之人笑之。盖曰今已晚也。无可报也。亦可忘也。凡冒富贵而湛溺声色者。从而和之曰然也。举漠然不以在心。亦独何哉。传曰。国君以国为体。故曰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然则我之于 皇明。虽百世苟为有国。当以国为之死。使虏酋犹有馀种。虽百世可伐也。古人有言曰。百世不可忘此贼。噫。此贼其可忘乎。向使尹尚书郑侍郎洪学士之谋得用。而悉朝鲜死力。以覆辽沈。则丑类歼而皇州可安。且焉有南汉之事。在南汉而使金相国郑侍郎尹学士吴学士之言得行。而城守有死国以义亡。则国中义士百群争死。虏必不能赖我而去。去必蹙伏。不敢犯 皇城。皇城之既陷也。我 宁考北伐之议得成。则天下方痛慕吾 君而恶丑虏。必斋应东师。四溃而奋发。必除虏乃已。顾天有未定。每误人事。使之痛伤羞抑。一至于此。而虏既据八域传四世。树本深坚。图之实难。乃今欲伐之者。若以时势则诚晚矣。若以时义则霅桥集卷四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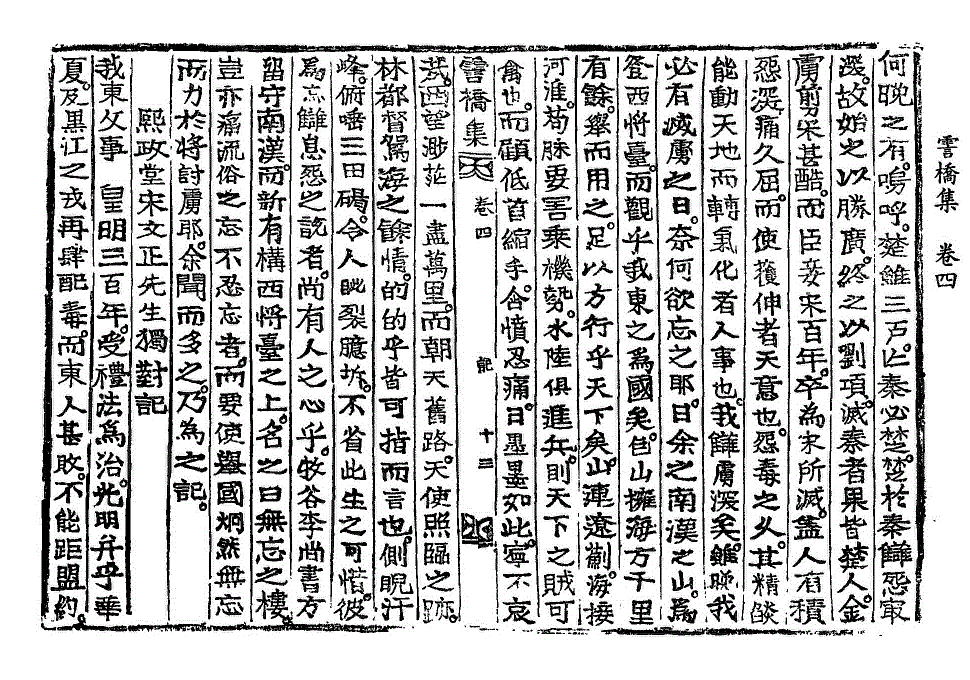 何晚之有。呜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于秦雠怨最深。故始之以胜广。终之以刘项。灭秦者果皆楚人。金虏剪宋甚酷。而臣妾宋百年。卒为宋所灭。盖人有积怨深痛久屈。而使获伸者天意也。怨毒之久。其精燄能动天地而转气化者人事也。我雠虏深矣。虽晚我必有灭虏之日。奈何欲忘之耶。日余之南汉之山。为登西将台。而观乎我东之为国矣。包山拥海方千里有馀。举而用之。足以方行乎天下矣。山连辽蓟。海接河淮。苟脉要害乘机势。水陆俱进兵。则天下之贼可禽也。而顾低首缩手。含愤忍痛。日墨墨如此。宁不哀哉。西望渺茫一尽万里。而朝天旧路。天使照临之迹。林都督驾海之馀情。的的乎皆可指而言也。侧睨汗峰。俯唾三田碣。令人眦裂臆坼。不省此生之可惜。彼为忘雠息怨之说者。尚有人之心乎。牧谷李尚书方留守南汉。而新有构西将台之上。名之曰无忘之楼。岂亦痛流俗之忘不忍忘者。而要使举国炯然无忘而力于将讨虏耶。余闻而多之。乃为之记。
何晚之有。呜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于秦雠怨最深。故始之以胜广。终之以刘项。灭秦者果皆楚人。金虏剪宋甚酷。而臣妾宋百年。卒为宋所灭。盖人有积怨深痛久屈。而使获伸者天意也。怨毒之久。其精燄能动天地而转气化者人事也。我雠虏深矣。虽晚我必有灭虏之日。奈何欲忘之耶。日余之南汉之山。为登西将台。而观乎我东之为国矣。包山拥海方千里有馀。举而用之。足以方行乎天下矣。山连辽蓟。海接河淮。苟脉要害乘机势。水陆俱进兵。则天下之贼可禽也。而顾低首缩手。含愤忍痛。日墨墨如此。宁不哀哉。西望渺茫一尽万里。而朝天旧路。天使照临之迹。林都督驾海之馀情。的的乎皆可指而言也。侧睨汗峰。俯唾三田碣。令人眦裂臆坼。不省此生之可惜。彼为忘雠息怨之说者。尚有人之心乎。牧谷李尚书方留守南汉。而新有构西将台之上。名之曰无忘之楼。岂亦痛流俗之忘不忍忘者。而要使举国炯然无忘而力于将讨虏耶。余闻而多之。乃为之记。熙政堂宋文正先生独对记
我东父事 皇明三百年。受礼法为治。光明并乎华夏。及黑江之戎再肆配毒。而东人甚败。不能距盟约。
霅桥集卷四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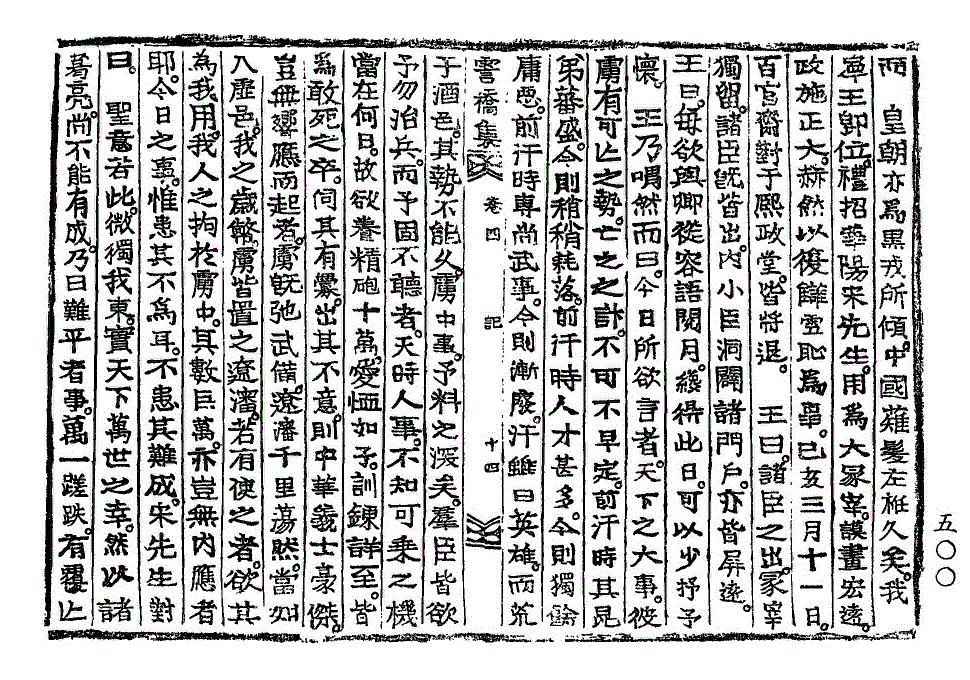 而 皇朝亦为黑戎所倾。中国薙发左衽久矣。我 宁王即位。礼招华阳宋先生。用为大冢宰。谟画宏远。政施正大。赫然以复雠雪耻为事。己亥三月十一日。百官斋对于熙政堂。皆将退。 王曰。诸臣之出。冢宰独留。诸臣既皆出。内小臣洞辟诸门户。亦皆屏远。 王曰。每欲与卿从容语阅月。才得此日。可以少抒予怀。 王乃喟然而曰。今日所欲言者。天下之大事。彼虏有可亡之势。亡之之计。不可不早定。前汗时其昆弟蕃盛。今则稍稍耗落。前汗时人才甚多。今则独馀庸恶。前汗时专尚武事。今则渐废。汗虽曰英雄。而荒于酒色。其势不能久。虏中事。予料之深矣。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可乘之机当在何日。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训鍊详至。皆为敢死之卒。伺其有衅。出其不意。则中华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而起者。虏既弛武备。辽沈千里荡然。当如入虚邑。我之岁幤。虏皆置之辽沈。若有使之者。欲其为我用。我人之拘于虏中。其数巨万。亦岂无内应者耶。今日之事。惟患其不为耳。不患其难成。宋先生对曰。 圣意若此。微独我东。实天下万世之幸。然以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难平者事。万一蹉跌。有覆亡
而 皇朝亦为黑戎所倾。中国薙发左衽久矣。我 宁王即位。礼招华阳宋先生。用为大冢宰。谟画宏远。政施正大。赫然以复雠雪耻为事。己亥三月十一日。百官斋对于熙政堂。皆将退。 王曰。诸臣之出。冢宰独留。诸臣既皆出。内小臣洞辟诸门户。亦皆屏远。 王曰。每欲与卿从容语阅月。才得此日。可以少抒予怀。 王乃喟然而曰。今日所欲言者。天下之大事。彼虏有可亡之势。亡之之计。不可不早定。前汗时其昆弟蕃盛。今则稍稍耗落。前汗时人才甚多。今则独馀庸恶。前汗时专尚武事。今则渐废。汗虽曰英雄。而荒于酒色。其势不能久。虏中事。予料之深矣。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可乘之机当在何日。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训鍊详至。皆为敢死之卒。伺其有衅。出其不意。则中华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而起者。虏既弛武备。辽沈千里荡然。当如入虚邑。我之岁幤。虏皆置之辽沈。若有使之者。欲其为我用。我人之拘于虏中。其数巨万。亦岂无内应者耶。今日之事。惟患其不为耳。不患其难成。宋先生对曰。 圣意若此。微独我东。实天下万世之幸。然以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难平者事。万一蹉跌。有覆亡霅桥集卷四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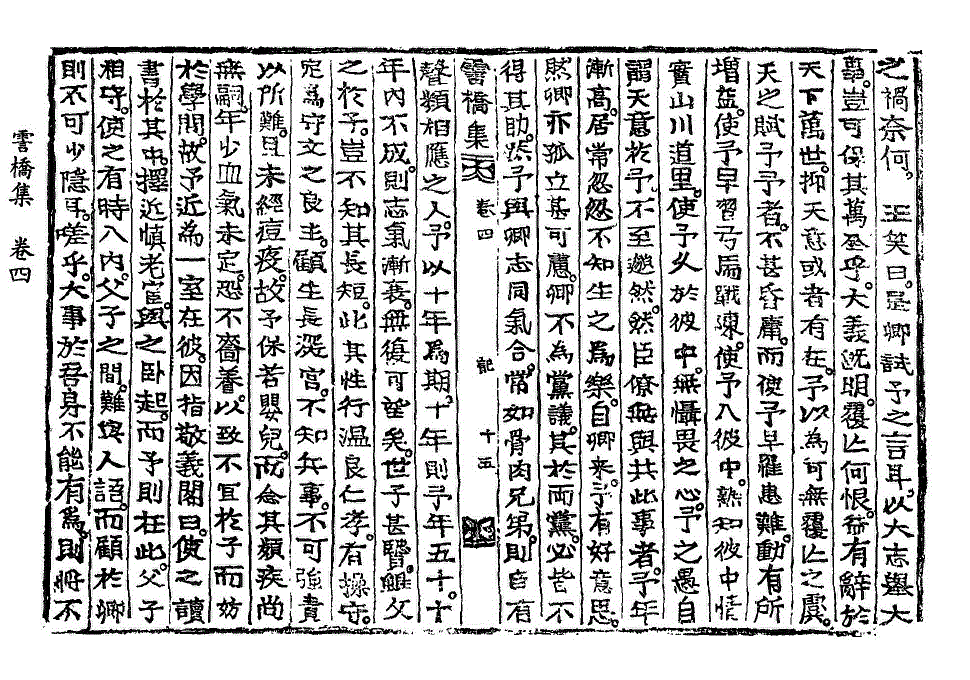 之祸奈何。 王笑曰。是卿试予之言耳。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乎。大义既明。覆亡何恨。益有辞于天下万世。抑天意或者有在。予以为可无覆亡之虞。天之赋予予者。不甚昏庸。而使予早罹患难。动有所增益。使予早习弓马战陈。使予入彼中。熟知彼中情实山川道里。使予久于彼中。无慑畏之心。予之愚自谓天意于予。不至邈然。然臣僚无与共此事者。予年渐高。居常忽忽不知生之为乐。自卿来。予有好意思。然卿亦孤立甚可虑。卿不为党议。其于两党。必皆不得其助。然予与卿志同气合。常如骨肉兄弟。则自有声类相应之人。予以十年为期。十年则予年五十。十年内不成。则志气渐衰。无复可望矣。世子甚贤。虽父之于子。岂不知其长短。此其性行温良仁孝。有操守。定为守文之良主。顾生长深宫。不知兵事。不可强责以所难。且未经痘疫。故予保若婴儿。而念其频疾尚无嗣。年少血气未定。恐不啬养。以致不宜于子而妨于学问。故予近为一室在彼。因指敬义阁曰。使之读书于其中。择近慎老宦。与之卧起。而予则在此。父子相守。使之有时入内。父子之间。难与人语。而顾于卿则不可少隐耳。嗟乎。大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
之祸奈何。 王笑曰。是卿试予之言耳。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乎。大义既明。覆亡何恨。益有辞于天下万世。抑天意或者有在。予以为可无覆亡之虞。天之赋予予者。不甚昏庸。而使予早罹患难。动有所增益。使予早习弓马战陈。使予入彼中。熟知彼中情实山川道里。使予久于彼中。无慑畏之心。予之愚自谓天意于予。不至邈然。然臣僚无与共此事者。予年渐高。居常忽忽不知生之为乐。自卿来。予有好意思。然卿亦孤立甚可虑。卿不为党议。其于两党。必皆不得其助。然予与卿志同气合。常如骨肉兄弟。则自有声类相应之人。予以十年为期。十年则予年五十。十年内不成。则志气渐衰。无复可望矣。世子甚贤。虽父之于子。岂不知其长短。此其性行温良仁孝。有操守。定为守文之良主。顾生长深宫。不知兵事。不可强责以所难。且未经痘疫。故予保若婴儿。而念其频疾尚无嗣。年少血气未定。恐不啬养。以致不宜于子而妨于学问。故予近为一室在彼。因指敬义阁曰。使之读书于其中。择近慎老宦。与之卧起。而予则在此。父子相守。使之有时入内。父子之间。难与人语。而顾于卿则不可少隐耳。嗟乎。大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霅桥集卷四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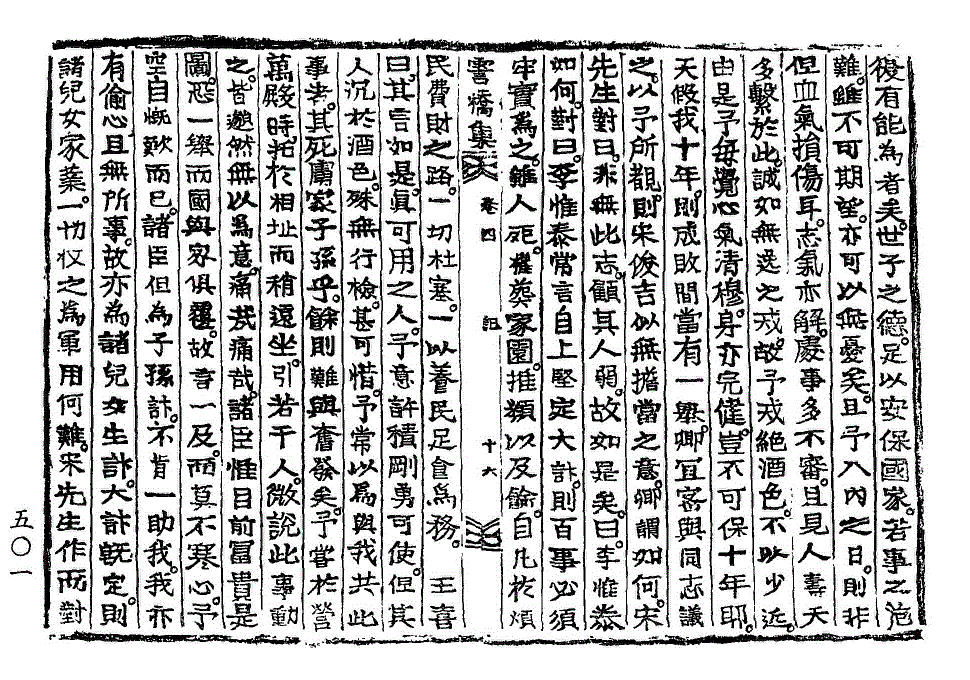 复有能为者矣。世子之德。足以安保国家。若事之危难。虽不可期望。亦可以无忧矣。且予入内之日。则非但血气损伤耳。志气亦解。处事多不审。且见人寿夭多系于此。诚如无逸之戒。故予戒绝酒色。不以少近。由是予每觉心气清穆。身亦完健。岂不可保十年耶。天假我十年。则成败间当有一举。卿宜密与同志议之。以予所睹。则宋俊吉似无担当之意。卿谓如何。宋先生对曰。非无此志。顾其人弱。故如是矣。曰。李惟泰如何。对曰。李惟泰常言自上坚定大计。则百事必须牢实为之。虽人死。权葬家园。推类以及馀。自凡于烦民费财之路。一切杜塞。一以养民足食为务。 王喜曰。其言如是。真可用之人。予意许积刚勇可使。但其人沉于酒色。殊无行检。甚可惜。予常以为与我共此事者。其死虏家子孙乎。馀则难与奋发矣。予尝于营万殿时。托于相址而稍远坐。引若干人。微说此事动之。皆邈然无以为意。痛哉痛哉。诸臣惟目前富贵是图。恐一举而国与家俱覆。故言一及。而莫不寒心。予空自慨叹而已。诸臣但为子孙计。不肯一助我。我亦有偷心。且无所事。故亦为诸儿女生计。大计既定。则诸儿女家业。一切收之为军用何难。宋先生作而对
复有能为者矣。世子之德。足以安保国家。若事之危难。虽不可期望。亦可以无忧矣。且予入内之日。则非但血气损伤耳。志气亦解。处事多不审。且见人寿夭多系于此。诚如无逸之戒。故予戒绝酒色。不以少近。由是予每觉心气清穆。身亦完健。岂不可保十年耶。天假我十年。则成败间当有一举。卿宜密与同志议之。以予所睹。则宋俊吉似无担当之意。卿谓如何。宋先生对曰。非无此志。顾其人弱。故如是矣。曰。李惟泰如何。对曰。李惟泰常言自上坚定大计。则百事必须牢实为之。虽人死。权葬家园。推类以及馀。自凡于烦民费财之路。一切杜塞。一以养民足食为务。 王喜曰。其言如是。真可用之人。予意许积刚勇可使。但其人沉于酒色。殊无行检。甚可惜。予常以为与我共此事者。其死虏家子孙乎。馀则难与奋发矣。予尝于营万殿时。托于相址而稍远坐。引若干人。微说此事动之。皆邈然无以为意。痛哉痛哉。诸臣惟目前富贵是图。恐一举而国与家俱覆。故言一及。而莫不寒心。予空自慨叹而已。诸臣但为子孙计。不肯一助我。我亦有偷心。且无所事。故亦为诸儿女生计。大计既定。则诸儿女家业。一切收之为军用何难。宋先生作而对霅桥集卷四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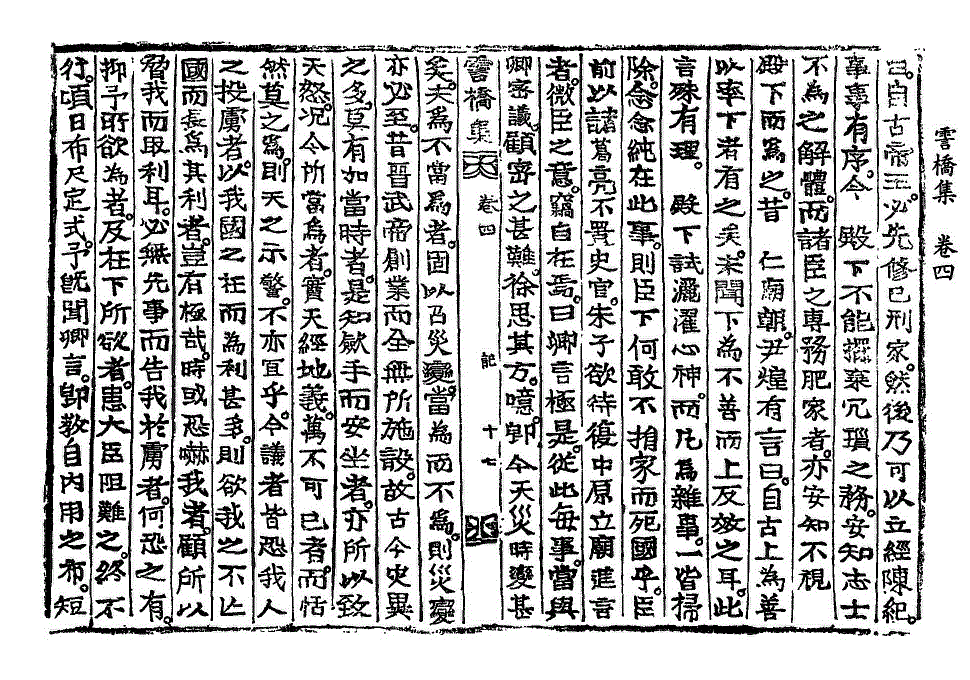 曰。自古帝王。必先修己刑家。然后乃可以立经陈纪。事事有序。今 殿下不能摆弃冗琐之务。安知志士不为之解体。而诸臣之专务肥家者。亦安知不视 殿下而为之。昔 仁庙朝。尹煌有言曰。自古上为善以率下者有之矣。未闻下为不善而上反效之耳。此言殊有理。 殿下试洒濯心神。而凡为杂事。一皆扫除。念念纯在此事。则臣下何敢不捐家而死国乎。臣前以诸葛亮不置史官。朱子欲待复中原立庙进言者。微臣之意。窃自在焉。曰卿言极是。从此每事。当与卿密议。顾密之甚难。徐思其方。噫。即今天灾时变甚矣。夫为不当为者。固以召灾变。当为而不为。则灾变亦必至。昔晋武帝创业而全无所施设。故古今灾异之多。莫有如当时者。是知敛手而安坐者。亦所以致天怒。况今所当为者。实天经地义。万不可已者。而恬然莫之为。则天之示警。不亦宜乎。今议者皆恐我人之投虏者。以我国之在而为利甚多。则欲我之不亡国而长为其利者。岂有极哉。时或恐吓我者。顾所以胁我而取利耳。必无先事而告我于虏者。何恐之有。抑予所欲为者。及在下所欲者。患大臣阻难之。终不行。顷日布尺定式。予既闻卿言。即教自内用之布。短
曰。自古帝王。必先修己刑家。然后乃可以立经陈纪。事事有序。今 殿下不能摆弃冗琐之务。安知志士不为之解体。而诸臣之专务肥家者。亦安知不视 殿下而为之。昔 仁庙朝。尹煌有言曰。自古上为善以率下者有之矣。未闻下为不善而上反效之耳。此言殊有理。 殿下试洒濯心神。而凡为杂事。一皆扫除。念念纯在此事。则臣下何敢不捐家而死国乎。臣前以诸葛亮不置史官。朱子欲待复中原立庙进言者。微臣之意。窃自在焉。曰卿言极是。从此每事。当与卿密议。顾密之甚难。徐思其方。噫。即今天灾时变甚矣。夫为不当为者。固以召灾变。当为而不为。则灾变亦必至。昔晋武帝创业而全无所施设。故古今灾异之多。莫有如当时者。是知敛手而安坐者。亦所以致天怒。况今所当为者。实天经地义。万不可已者。而恬然莫之为。则天之示警。不亦宜乎。今议者皆恐我人之投虏者。以我国之在而为利甚多。则欲我之不亡国而长为其利者。岂有极哉。时或恐吓我者。顾所以胁我而取利耳。必无先事而告我于虏者。何恐之有。抑予所欲为者。及在下所欲者。患大臣阻难之。终不行。顷日布尺定式。予既闻卿言。即教自内用之布。短霅桥集卷四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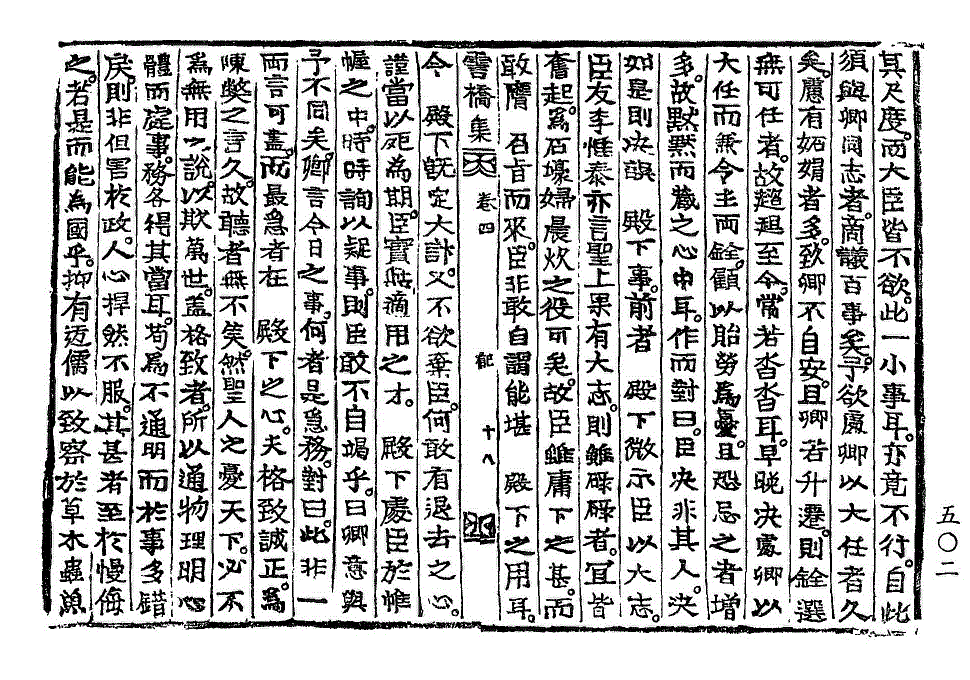 其尺度。而大臣皆不欲。此一小事耳。亦竟不行。自此须与卿同志者。商议百事矣。予欲处卿以大任者久矣。虑有妒媢者多。致卿不自安。且卿若升迁。则铨选无可任者。故趑趄至今。常若沓沓耳。早晚决处卿以大任而兼令主两铨。顾以贻劳为忧。且恐忌之者增多。故默默而藏之心中耳。作而对曰。臣决非其人。决如是则决误 殿下事。前者 殿下微示臣以大志。臣友李惟泰亦言圣上果有大志。则虽碌碌者。宜皆奋起。为石壕妇晨炊之役可矣。故臣虽庸下之甚。而敢膺 召旨而来。臣非敢自谓能堪 殿下之用耳。今 殿下既定大计。又不欲弃臣。何敢有退去之心。谨当以死为期。臣实无适用之才。 殿下处臣于帷幄之中。时时询以疑事。则臣敢不自竭乎。曰卿意与予不同矣。卿言今日之事。何者是急务。对曰。此非一两言可尽。而最急者在 殿下之心。夫格致诚正。为陈弊之言久。故听者无不笑。然圣人之忧天下。必不为无用之说。以欺万世。盖格致者。所以通物理明心体而处事。务各得其当耳。苟为不通明而于事多错戾。则非但害于政。人心捍然不服。其甚者至于慢侮之。若是而能为国乎。抑有迂儒以致察于草木虫鱼
其尺度。而大臣皆不欲。此一小事耳。亦竟不行。自此须与卿同志者。商议百事矣。予欲处卿以大任者久矣。虑有妒媢者多。致卿不自安。且卿若升迁。则铨选无可任者。故趑趄至今。常若沓沓耳。早晚决处卿以大任而兼令主两铨。顾以贻劳为忧。且恐忌之者增多。故默默而藏之心中耳。作而对曰。臣决非其人。决如是则决误 殿下事。前者 殿下微示臣以大志。臣友李惟泰亦言圣上果有大志。则虽碌碌者。宜皆奋起。为石壕妇晨炊之役可矣。故臣虽庸下之甚。而敢膺 召旨而来。臣非敢自谓能堪 殿下之用耳。今 殿下既定大计。又不欲弃臣。何敢有退去之心。谨当以死为期。臣实无适用之才。 殿下处臣于帷幄之中。时时询以疑事。则臣敢不自竭乎。曰卿意与予不同矣。卿言今日之事。何者是急务。对曰。此非一两言可尽。而最急者在 殿下之心。夫格致诚正。为陈弊之言久。故听者无不笑。然圣人之忧天下。必不为无用之说。以欺万世。盖格致者。所以通物理明心体而处事。务各得其当耳。苟为不通明而于事多错戾。则非但害于政。人心捍然不服。其甚者至于慢侮之。若是而能为国乎。抑有迂儒以致察于草木虫鱼霅桥集卷四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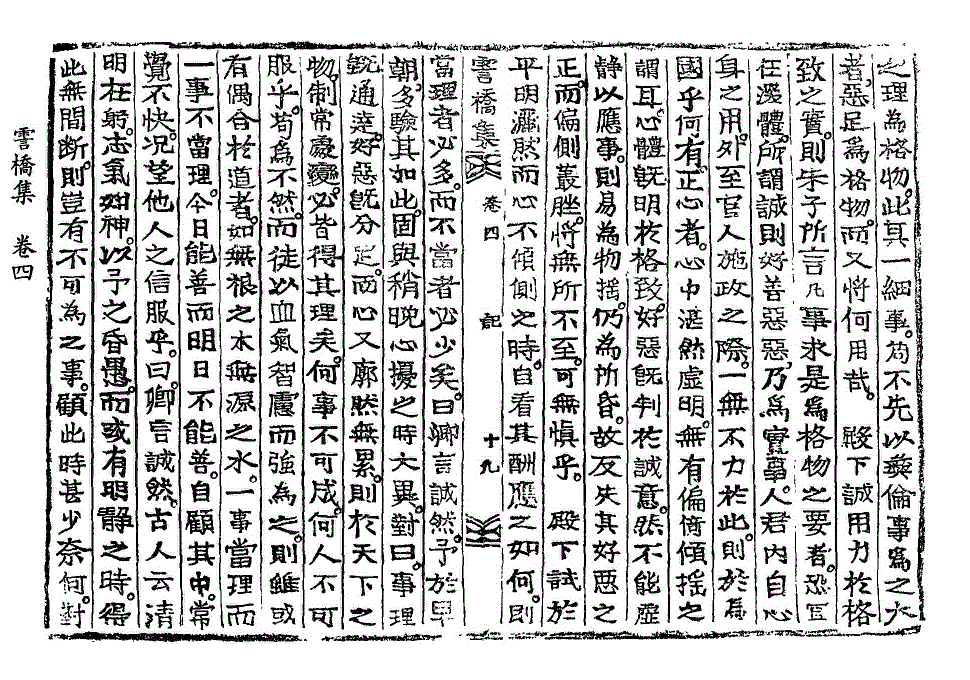 之理为格物。此其一细事。苟不先以彝伦事为之大者。恶足为格物。而又将何用哉。 殿下诚用力于格致之实。则朱子所言凡事求是为格物之要者。恐宜在深体。所谓诚则好善恶恶。乃为实事。人君内自心身之用。外至官人施政之际。一无不力于此。则于为国乎何有。正心者。心中湛然虚明。无有偏倚倾摇之谓耳。心体既明于格致。好恶既判于诚意。然不能虚静以应事。则易为物摇。仍为所昏。故反失其好恶之正。而偏侧丛脞。将无所不至。可无慎乎。 殿下试于平明洒然而心不倾侧之时。自看其酬应之如何。则当理者必多。而不当者必少矣。曰卿言诚然。予于早朝。多验其如此。固与稍晚心扰之时大异。对曰。事理既通达。好恶既分定。而心又廓然无累。则于天下之物。制常处变。必皆得其理矣。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服乎。苟为不然。而徒以血气智虑而强为之。则虽或有偶合于道者。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事当理而一事不当理。今日能善而明日不能善。自顾其中。常觉不快。况望他人之信服乎。曰。卿言诚然。古人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以予之昏愚。而或有明静之时。得此无间断。则岂有不可为之事。顾此时甚少奈何。对
之理为格物。此其一细事。苟不先以彝伦事为之大者。恶足为格物。而又将何用哉。 殿下诚用力于格致之实。则朱子所言凡事求是为格物之要者。恐宜在深体。所谓诚则好善恶恶。乃为实事。人君内自心身之用。外至官人施政之际。一无不力于此。则于为国乎何有。正心者。心中湛然虚明。无有偏倚倾摇之谓耳。心体既明于格致。好恶既判于诚意。然不能虚静以应事。则易为物摇。仍为所昏。故反失其好恶之正。而偏侧丛脞。将无所不至。可无慎乎。 殿下试于平明洒然而心不倾侧之时。自看其酬应之如何。则当理者必多。而不当者必少矣。曰卿言诚然。予于早朝。多验其如此。固与稍晚心扰之时大异。对曰。事理既通达。好恶既分定。而心又廓然无累。则于天下之物。制常处变。必皆得其理矣。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服乎。苟为不然。而徒以血气智虑而强为之。则虽或有偶合于道者。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事当理而一事不当理。今日能善而明日不能善。自顾其中。常觉不快。况望他人之信服乎。曰。卿言诚然。古人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以予之昏愚。而或有明静之时。得此无间断。则岂有不可为之事。顾此时甚少奈何。对霅桥集卷四 第 503L 页
 曰。此程朱所以论学者。必以敬为主。敬则此心常存。无所间断。不敬则心中烦乱。而好意旋衰。故朱子曰。一时意思能得几时。即虽小事。非存心则不可成。况天下之大事乎。曰。卿每以至诚导予。予不敢忘。卿亦自思所以集众善来嘉言。以为共济之图。最卿平明之说甚切。予亦屡验之矣。事有拂于心者姑置之。待中夜不平之消然后。早起而处之。即其不当者果少。有以知孟子之言为至论。对曰。 殿下常如此用功。则圣学何忧乎不至于高明。 王曰。近有所大可闷者。当问于卿而决之。予于两贤从祀之论。常弥缝彼此。仅有安静之势。则又见忽起而风波大作。其害于事。何可胜言。卿意以为何是何非。对曰。臣有不敢易言。虽然。两贤从祀之请。一国同辞。今已数十年。可谓公论。惟若干人袭先议。敢为异同之说。臣意以为从祀是重典。容有所不可轻议。若诬辱两贤者。则决是悖乱之徒。甚可痛。曰。此辈诚是悖戾者。何足与校乎。对曰。此辈诚不足校。其父兄者。不能止之。反为指导。深可恶。若两贤道学。则臣亦末学。何敢与知。自上读其书求其心而论其行事之迹。则可知从祀之当与不当矣。若不能明知笃信。而惟人言是听。则虽极其崇奖之典。实无益于心身
曰。此程朱所以论学者。必以敬为主。敬则此心常存。无所间断。不敬则心中烦乱。而好意旋衰。故朱子曰。一时意思能得几时。即虽小事。非存心则不可成。况天下之大事乎。曰。卿每以至诚导予。予不敢忘。卿亦自思所以集众善来嘉言。以为共济之图。最卿平明之说甚切。予亦屡验之矣。事有拂于心者姑置之。待中夜不平之消然后。早起而处之。即其不当者果少。有以知孟子之言为至论。对曰。 殿下常如此用功。则圣学何忧乎不至于高明。 王曰。近有所大可闷者。当问于卿而决之。予于两贤从祀之论。常弥缝彼此。仅有安静之势。则又见忽起而风波大作。其害于事。何可胜言。卿意以为何是何非。对曰。臣有不敢易言。虽然。两贤从祀之请。一国同辞。今已数十年。可谓公论。惟若干人袭先议。敢为异同之说。臣意以为从祀是重典。容有所不可轻议。若诬辱两贤者。则决是悖乱之徒。甚可痛。曰。此辈诚是悖戾者。何足与校乎。对曰。此辈诚不足校。其父兄者。不能止之。反为指导。深可恶。若两贤道学。则臣亦末学。何敢与知。自上读其书求其心而论其行事之迹。则可知从祀之当与不当矣。若不能明知笃信。而惟人言是听。则虽极其崇奖之典。实无益于心身霅桥集卷四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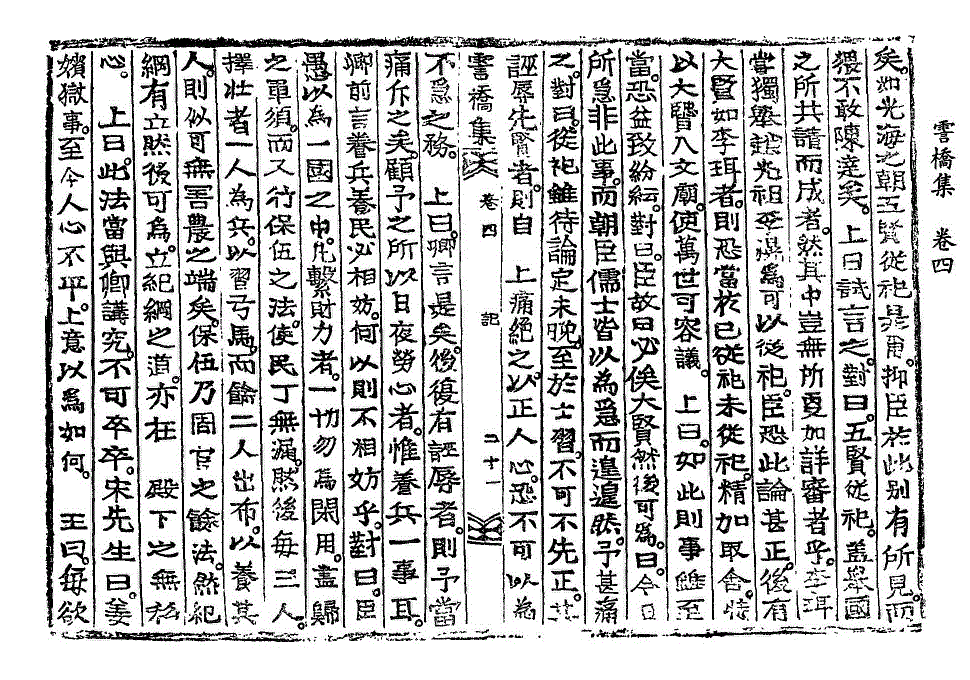 矣。如光海之朝五贤从祀是尔。抑臣于此别有所见。而猥不敢陈达矣。 上曰试言之。对曰。五贤从祀。盖举国之所共请而成者。然其中岂无所更加详审者乎。李珥尝独举赵光祖李滉为可以从祀。臣恐此论甚正。后有大贤如李珥者。则恐当于已从祀未从祀。精加取舍。特以大贤入文庙。使万世可容议。 上曰。如此则事虽至当。恐益致纷纭。对曰。臣故曰必俟大贤然后可为。曰。今日所急非此事。而朝臣儒士皆以为急而遑遑然。予甚痛之。对曰。从祀虽待论定未晚。至于士习。不可不先正。其诬辱先贤者。则自 上痛绝之。以正人心。恐不可以为不急之务。 上曰。卿言是矣。后复有诬辱者。则予当痛斥之矣。顾予之所以日夜劳心者。惟养兵一事耳。卿前言养兵养民必相妨。何以则不相妨乎。对曰。臣愚以为一国之中。凡系财力者。一切勿为闲用。尽归之军须。而又行保伍之法。使民丁无漏。然后每三人。择壮者一人为兵。以习弓马。而馀二人出布。以养其人。则似可无害农之端矣。保伍乃周官之馀法。然纪纲有立然后可为。立纪纲之道。亦在 殿下之无私心。 上曰。此法当与卿讲究。不可卒卒。宋先生曰。姜嫔狱事。至今人心不平。上意以为如何。 王曰。每欲
矣。如光海之朝五贤从祀是尔。抑臣于此别有所见。而猥不敢陈达矣。 上曰试言之。对曰。五贤从祀。盖举国之所共请而成者。然其中岂无所更加详审者乎。李珥尝独举赵光祖李滉为可以从祀。臣恐此论甚正。后有大贤如李珥者。则恐当于已从祀未从祀。精加取舍。特以大贤入文庙。使万世可容议。 上曰。如此则事虽至当。恐益致纷纭。对曰。臣故曰必俟大贤然后可为。曰。今日所急非此事。而朝臣儒士皆以为急而遑遑然。予甚痛之。对曰。从祀虽待论定未晚。至于士习。不可不先正。其诬辱先贤者。则自 上痛绝之。以正人心。恐不可以为不急之务。 上曰。卿言是矣。后复有诬辱者。则予当痛斥之矣。顾予之所以日夜劳心者。惟养兵一事耳。卿前言养兵养民必相妨。何以则不相妨乎。对曰。臣愚以为一国之中。凡系财力者。一切勿为闲用。尽归之军须。而又行保伍之法。使民丁无漏。然后每三人。择壮者一人为兵。以习弓马。而馀二人出布。以养其人。则似可无害农之端矣。保伍乃周官之馀法。然纪纲有立然后可为。立纪纲之道。亦在 殿下之无私心。 上曰。此法当与卿讲究。不可卒卒。宋先生曰。姜嫔狱事。至今人心不平。上意以为如何。 王曰。每欲霅桥集卷四 第 5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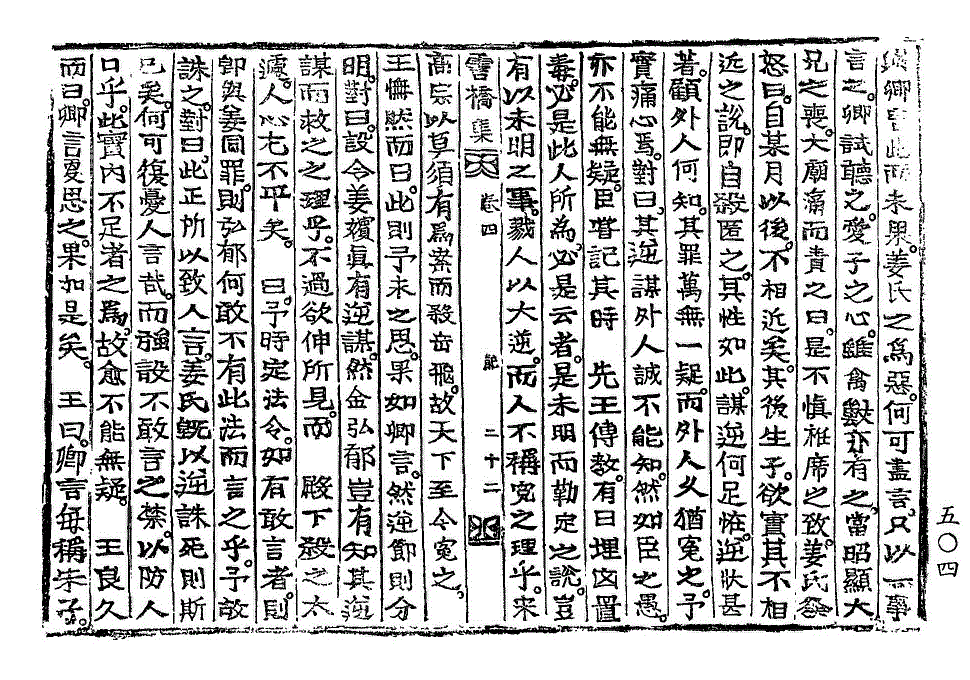 与卿言此而未果。姜氏之为恶。何可尽言。只以一事言之。卿试听之。爱子之心。虽禽兽亦有之。当昭显大兄之丧。大庙痛而责之曰。是不慎衽席之致。姜氏发怒曰。自某月以后。不相近矣。其后生子。欲实其不相近之说。即自杀匿之。其性如此。谋逆何足怪。逆状甚著。顾外人何知。其罪万无一疑。而外人久犹冤之。予实痛心焉。对曰。其逆谋外人诚不能知。然如臣之愚。亦不能无疑。臣尝记其时 先王传教。有曰埋凶置毒。必是此人所为。必是云者。是未明而勒定之说。岂有以未明之事。戮人以大逆。而人不称冤之理乎。宋高宗以莫须有为案而杀岳飞。故天下至今冤之。 王怃然而曰。此则予未之思。果如卿言。然逆节则分明。对曰。设令姜嫔真有逆谋。然金弘郁岂有知其逆谋而救之之理乎。不过欲伸所见。而 殿下杀之太遽。人心尤不平矣。 曰。予时定法令。如有敢言者。则即与姜同罪。则弘郁何敢不有此法而言之乎。予故诛之。对曰。此正所以致人言。姜氏既以逆诛死则斯已矣。何可复忧人言哉。而强设不敢言之禁。以防人口乎。此实内不足者之为。故愈不能无疑。 王良久而曰。卿言更思之。果如是矣。 王曰。卿言每称朱子。
与卿言此而未果。姜氏之为恶。何可尽言。只以一事言之。卿试听之。爱子之心。虽禽兽亦有之。当昭显大兄之丧。大庙痛而责之曰。是不慎衽席之致。姜氏发怒曰。自某月以后。不相近矣。其后生子。欲实其不相近之说。即自杀匿之。其性如此。谋逆何足怪。逆状甚著。顾外人何知。其罪万无一疑。而外人久犹冤之。予实痛心焉。对曰。其逆谋外人诚不能知。然如臣之愚。亦不能无疑。臣尝记其时 先王传教。有曰埋凶置毒。必是此人所为。必是云者。是未明而勒定之说。岂有以未明之事。戮人以大逆。而人不称冤之理乎。宋高宗以莫须有为案而杀岳飞。故天下至今冤之。 王怃然而曰。此则予未之思。果如卿言。然逆节则分明。对曰。设令姜嫔真有逆谋。然金弘郁岂有知其逆谋而救之之理乎。不过欲伸所见。而 殿下杀之太遽。人心尤不平矣。 曰。予时定法令。如有敢言者。则即与姜同罪。则弘郁何敢不有此法而言之乎。予故诛之。对曰。此正所以致人言。姜氏既以逆诛死则斯已矣。何可复忧人言哉。而强设不敢言之禁。以防人口乎。此实内不足者之为。故愈不能无疑。 王良久而曰。卿言更思之。果如是矣。 王曰。卿言每称朱子。霅桥集卷四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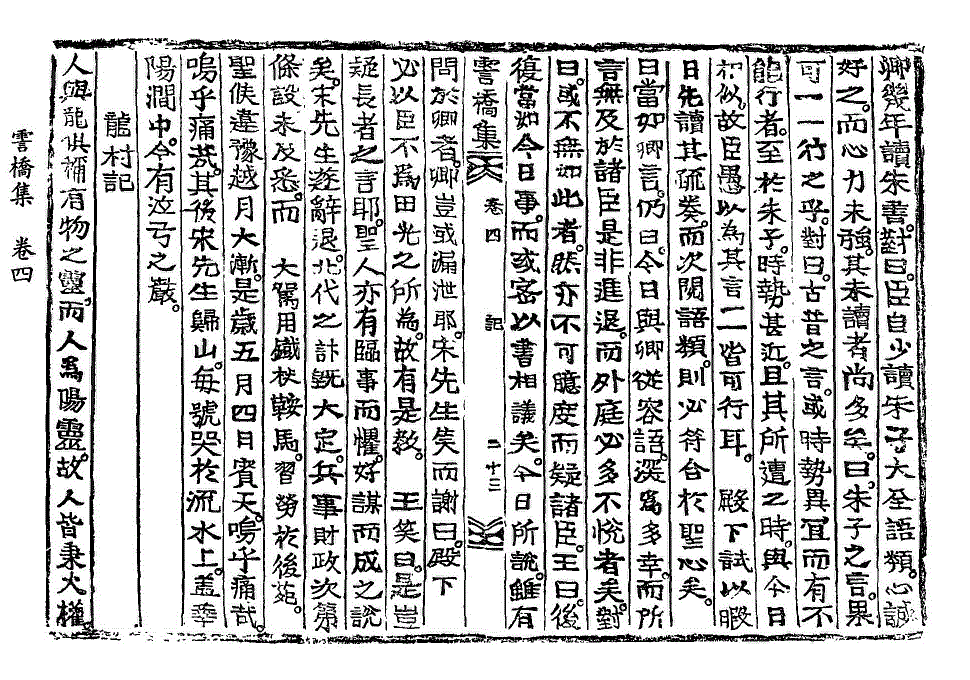 卿几年读朱书。对曰。臣自少读朱子大全语类。心诚好之。而心力未强。其未读者尚多矣。曰。朱子之言。果可一一行之乎。对曰。古昔之言。或时势异宜而有不能行者。至于朱子。时势甚近。且其所遭之时。与今日相似。故臣愚以为其言一一皆可行耳。 殿下试以暇日先读其疏奏。而次阅语类。则必符合于圣心矣。 曰当如卿言。仍曰。今日与卿从容语。深为多幸。而所言无及于诸臣是非进退。而外庭必多不悦者矣。对曰。或不无如此者。然亦不可臆度而疑诸臣。王曰。后复当如今日事。而或密以书相议矣。今日所说。虽有问于卿者。卿岂或漏泄耶。宋先生笑而谢曰。殿下 必以臣不为田光之所为。故有是教。 王笑曰。是岂疑长者之言耶。圣人亦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说矣。宋先生遂辞退。北伐之计既大定。兵事财政次第条设未及悉。而 大驾用铁杖鞍马。习劳于后苑。 圣候违豫越月大渐。是岁五月四日宾天。呜乎痛哉。呜乎痛哉。其后宋先生归山。每号哭于流水上。盖华阳涧中。今有泣弓之岩。
卿几年读朱书。对曰。臣自少读朱子大全语类。心诚好之。而心力未强。其未读者尚多矣。曰。朱子之言。果可一一行之乎。对曰。古昔之言。或时势异宜而有不能行者。至于朱子。时势甚近。且其所遭之时。与今日相似。故臣愚以为其言一一皆可行耳。 殿下试以暇日先读其疏奏。而次阅语类。则必符合于圣心矣。 曰当如卿言。仍曰。今日与卿从容语。深为多幸。而所言无及于诸臣是非进退。而外庭必多不悦者矣。对曰。或不无如此者。然亦不可臆度而疑诸臣。王曰。后复当如今日事。而或密以书相议矣。今日所说。虽有问于卿者。卿岂或漏泄耶。宋先生笑而谢曰。殿下 必以臣不为田光之所为。故有是教。 王笑曰。是岂疑长者之言耶。圣人亦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说矣。宋先生遂辞退。北伐之计既大定。兵事财政次第条设未及悉。而 大驾用铁杖鞍马。习劳于后苑。 圣候违豫越月大渐。是岁五月四日宾天。呜乎痛哉。呜乎痛哉。其后宋先生归山。每号哭于流水上。盖华阳涧中。今有泣弓之岩。龙村记
人与龙俱称有物之灵。而人为阳灵。故人皆秉火权。
霅桥集卷四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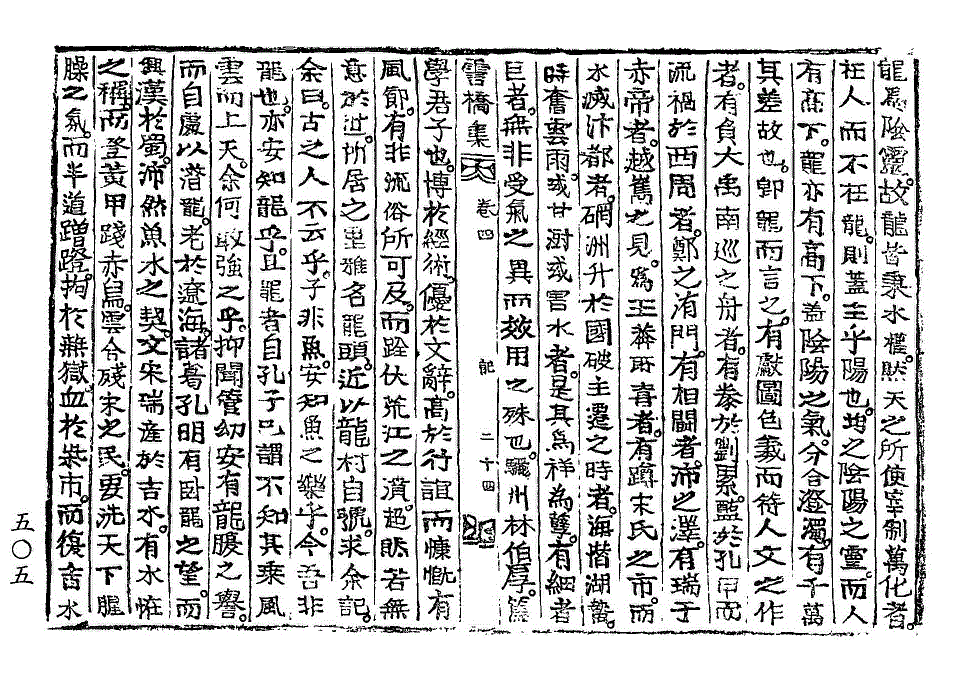 龙为阴灵。故龙皆秉水权。然天之所使宰制万化者。在人而不在龙。则盖主乎阳也。均之阴阳之灵。而人有高下。龙亦有高下。盖阴阳之气。分合澄浊。有千万其差故也。即龙而言之。有献图包羲而符人文之作者。有负大禹南巡之舟者。有豢于刘累。醢于孔甲而流祸于西周者。郑之洧门。有相斗者。沛之泽。有瑞于赤帝者。越巂之见。为王莽所喜者。有蹲宋氏之市。而水灭汴都者。䃃洲升于国破主迁之时者。海潜湖蛰。时奋云雨。或甘澍或害水者。是其为祥为孽。有细者巨者。无非受气之异而效用之殊也。骊州林伯厚。笃学君子也。博于经术。优于文辞。高于行谊而慷慨有风节。有非流俗所可及。而跧伏荒江之濆。超然若无意于世。所居之里雅名龙头。近以龙村自号。求余记。余曰。古之人不云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今吾非龙也。亦安知龙乎。且龙者自孔子已谓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余何敢强之乎。抑闻管幼安有龙腹之誉。而自处以潜龙。老于辽海。诸葛孔明有卧龙之望。而兴汉于蜀。沛然鱼水之契。文宋瑞产于吉水。有水怪之称。而登黄甲践赤舄。云合残宋之民。要洗天下腥臊之氛。而半道蹭蹬。拘于燕狱。血于柴市。而复吉水
龙为阴灵。故龙皆秉水权。然天之所使宰制万化者。在人而不在龙。则盖主乎阳也。均之阴阳之灵。而人有高下。龙亦有高下。盖阴阳之气。分合澄浊。有千万其差故也。即龙而言之。有献图包羲而符人文之作者。有负大禹南巡之舟者。有豢于刘累。醢于孔甲而流祸于西周者。郑之洧门。有相斗者。沛之泽。有瑞于赤帝者。越巂之见。为王莽所喜者。有蹲宋氏之市。而水灭汴都者。䃃洲升于国破主迁之时者。海潜湖蛰。时奋云雨。或甘澍或害水者。是其为祥为孽。有细者巨者。无非受气之异而效用之殊也。骊州林伯厚。笃学君子也。博于经术。优于文辞。高于行谊而慷慨有风节。有非流俗所可及。而跧伏荒江之濆。超然若无意于世。所居之里雅名龙头。近以龙村自号。求余记。余曰。古之人不云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今吾非龙也。亦安知龙乎。且龙者自孔子已谓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余何敢强之乎。抑闻管幼安有龙腹之誉。而自处以潜龙。老于辽海。诸葛孔明有卧龙之望。而兴汉于蜀。沛然鱼水之契。文宋瑞产于吉水。有水怪之称。而登黄甲践赤舄。云合残宋之民。要洗天下腥臊之氛。而半道蹭蹬。拘于燕狱。血于柴市。而复吉水霅桥集卷四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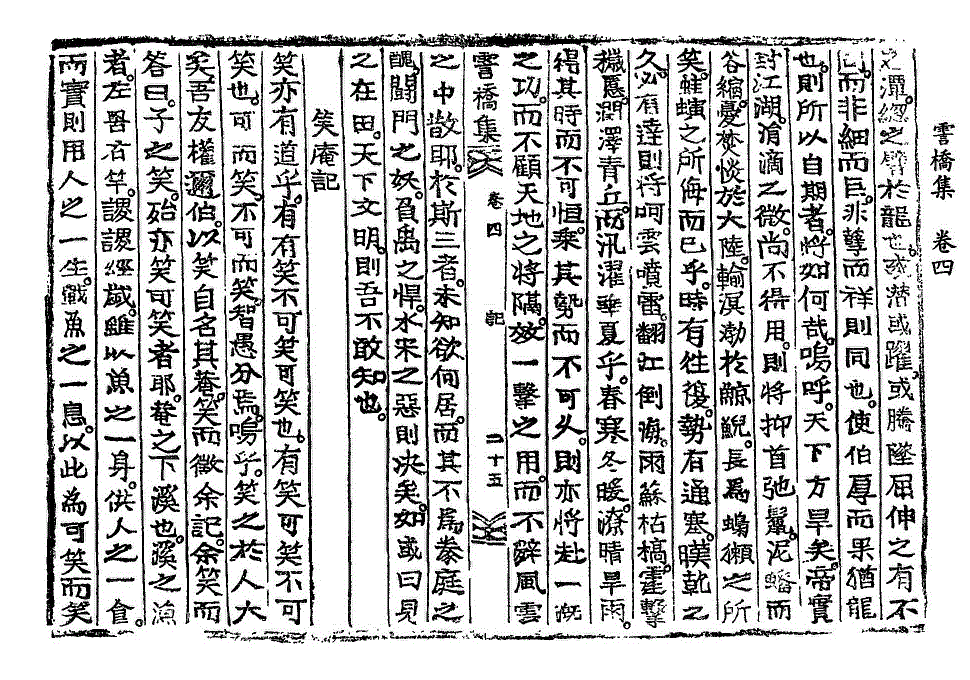 之潭。总之譬于龙也。或潜或跃。或腾坠屈伸之有不同。而非细而巨。非孽而祥则同也。使伯厚而果犹龙也。则所以自期者。将如何哉。呜呼。天下方旱矣。帝实封江湖。涓滴之微。尚不得用。则将抑首弛鬣。泥蟠而谷缩。忧焚惔于大陆。输溟渤于鲸鲵。长为蟂獭之所笑。蛙螾之所侮而已乎。时有往复。势有通塞。暵乾之久。必有达则将呵云喷雷。翻江倒海。雨苏枯槁。霆击秽慝。润泽青丘。而汛濯华夏乎。春寒冬暖。潦晴旱雨。得其时而不可恒。乘其势而不可久。则亦将赴一溉之功。而不顾天地之将隔。效一击之用。而不辞风云之中散耶。于斯三者。未知欲何居。而其不为豢庭之丑。斗门之妖。负禹之悍。水宋之恶则决矣。如或曰见之在田。天下文明。则吾不敢知也。
之潭。总之譬于龙也。或潜或跃。或腾坠屈伸之有不同。而非细而巨。非孽而祥则同也。使伯厚而果犹龙也。则所以自期者。将如何哉。呜呼。天下方旱矣。帝实封江湖。涓滴之微。尚不得用。则将抑首弛鬣。泥蟠而谷缩。忧焚惔于大陆。输溟渤于鲸鲵。长为蟂獭之所笑。蛙螾之所侮而已乎。时有往复。势有通塞。暵乾之久。必有达则将呵云喷雷。翻江倒海。雨苏枯槁。霆击秽慝。润泽青丘。而汛濯华夏乎。春寒冬暖。潦晴旱雨。得其时而不可恒。乘其势而不可久。则亦将赴一溉之功。而不顾天地之将隔。效一击之用。而不辞风云之中散耶。于斯三者。未知欲何居。而其不为豢庭之丑。斗门之妖。负禹之悍。水宋之恶则决矣。如或曰见之在田。天下文明。则吾不敢知也。笑庵记
笑亦有道乎。有有笑不可笑可笑也。有笑可笑不可笑也。可而笑。不可而笑。智愚分焉。呜乎。笑之于人大矣。吾友权迩伯。以笑自名其庵。笑而徵余记。余笑而答曰。子之笑。殆亦笑可笑者耶。庵之下溪也。溪之渔者。左罟右竿。谡谡经岁。虽以鱼之一身。供人之一食。而实则用人之一生。战鱼之一息。以此为可笑而笑
霅桥集卷四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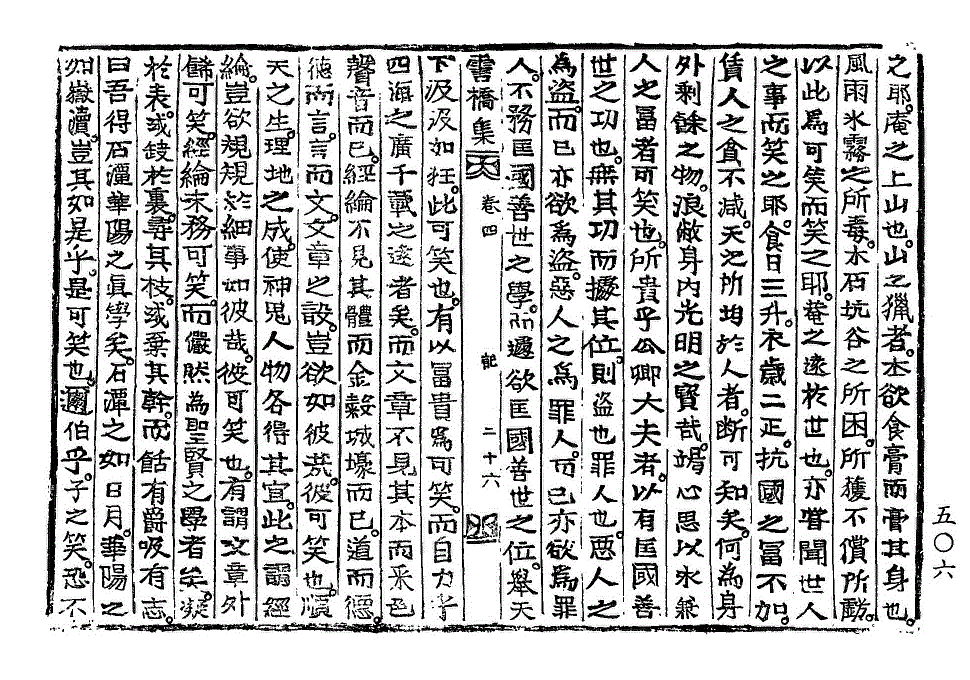 之耶。庵之上山也。山之猎者。本欲食膏而膏其身也。风雨冰雾之所毒。木石坑谷之所困。所获不偿所亏。以此为可笑而笑之耶。庵之远于世也。亦尝闻世人之事而笑之耶。食日三升。衣岁二疋。抗国之富不加。赁人之贫不减。天之所均于人者。断可知矣。何为身外剩馀之物。浪敝身内光明之宝哉。竭心思以求兼人之富者可笑也。所贵乎公卿大夫者。以有匡国善世之功也。无其功而据其位。则盗也罪人也。恶人之为盗。而己亦欲为盗。恶人之为罪人。而己亦欲为罪人。不务匡国善世之学。而遽欲匡国善世之位。举天下汲汲如狂。此可笑也。有以富贵为可笑。而自力乎四海之广千载之远者矣。而文章不见其本而采色声音而已。经纶不见其体而金谷城壕而已。道而德。德而言。言而文。文章之设。岂欲如彼哉。彼可笑也。顺天之生。理地之成。使神鬼人物各得其宜。此之谓经纶。岂欲规规于细事如彼哉。彼可笑也。有谓文章外饰可笑。经纶末务可笑。而俨然为圣贤之学者矣。凝于表。或缺于里。寻其枝。或弃其干。而餂有爵吸有志。曰吾得石潭华阳之真学矣。石潭之如日月。华阳之如岳渎。岂其如是乎。是可笑也。迩伯乎。子之笑。恐不
之耶。庵之上山也。山之猎者。本欲食膏而膏其身也。风雨冰雾之所毒。木石坑谷之所困。所获不偿所亏。以此为可笑而笑之耶。庵之远于世也。亦尝闻世人之事而笑之耶。食日三升。衣岁二疋。抗国之富不加。赁人之贫不减。天之所均于人者。断可知矣。何为身外剩馀之物。浪敝身内光明之宝哉。竭心思以求兼人之富者可笑也。所贵乎公卿大夫者。以有匡国善世之功也。无其功而据其位。则盗也罪人也。恶人之为盗。而己亦欲为盗。恶人之为罪人。而己亦欲为罪人。不务匡国善世之学。而遽欲匡国善世之位。举天下汲汲如狂。此可笑也。有以富贵为可笑。而自力乎四海之广千载之远者矣。而文章不见其本而采色声音而已。经纶不见其体而金谷城壕而已。道而德。德而言。言而文。文章之设。岂欲如彼哉。彼可笑也。顺天之生。理地之成。使神鬼人物各得其宜。此之谓经纶。岂欲规规于细事如彼哉。彼可笑也。有谓文章外饰可笑。经纶末务可笑。而俨然为圣贤之学者矣。凝于表。或缺于里。寻其枝。或弃其干。而餂有爵吸有志。曰吾得石潭华阳之真学矣。石潭之如日月。华阳之如岳渎。岂其如是乎。是可笑也。迩伯乎。子之笑。恐不霅桥集卷四 第 507H 页
 可笑也。其笑此五者之可笑乎。迩伯仰天而笑曰。吾岂笑人者乎。受人之笑者也。吾于此庵。闭门独卧。不干于人。不知有富贵之可图。文章之可尚。经纶之可讲。圣贤之学之可为。凡世之显名厚利隆权重势。顾挤之于一枕之外。世人皆笑之。看山而山禽得得如也。吾则开一笑而已。临水而水鱼泼泼如也。吾亦开一笑而已。渔者之多术。猎者之多勇。又皆笑吾之痴劣不能谋食。吾皆欣然受其笑。而实亦自笑也。故笑而命庵名以笑。呜乎。以吾之不暇于自笑。而受笑于人也。顾奚暇笑人。余洒然不觉敛笑而曰。子其过人乎哉。人之多可笑而笑之者无可笑。则子初不以为笑。子之无可笑而笑之者乃可笑。则子安而受其笑。子其过人乎哉。真可谓得笑之道矣。向吾之言。吾其受子之笑。遂笑而书之。为笑庵记。
可笑也。其笑此五者之可笑乎。迩伯仰天而笑曰。吾岂笑人者乎。受人之笑者也。吾于此庵。闭门独卧。不干于人。不知有富贵之可图。文章之可尚。经纶之可讲。圣贤之学之可为。凡世之显名厚利隆权重势。顾挤之于一枕之外。世人皆笑之。看山而山禽得得如也。吾则开一笑而已。临水而水鱼泼泼如也。吾亦开一笑而已。渔者之多术。猎者之多勇。又皆笑吾之痴劣不能谋食。吾皆欣然受其笑。而实亦自笑也。故笑而命庵名以笑。呜乎。以吾之不暇于自笑。而受笑于人也。顾奚暇笑人。余洒然不觉敛笑而曰。子其过人乎哉。人之多可笑而笑之者无可笑。则子初不以为笑。子之无可笑而笑之者乃可笑。则子安而受其笑。子其过人乎哉。真可谓得笑之道矣。向吾之言。吾其受子之笑。遂笑而书之。为笑庵记。长厚堂记
天长地厚。履载无彊。究其所以。则惟健顺生生之德是已。以其生生而健也。故能长于覆物。以其生生而顺也。故能厚于载物。呜呼。物之最灵而学于天地者。修其所受。当如何哉。吾友郑伯玉。生于忠州之长厚院。好学几于有立。吾为之因里名。名其读书之堂长
霅桥集卷四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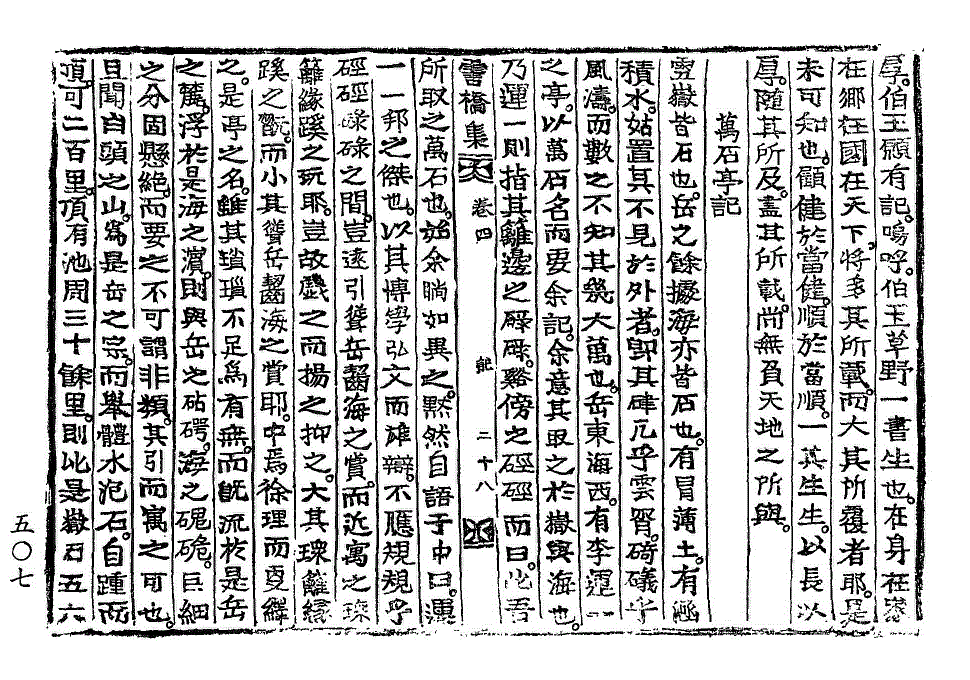 厚。伯玉愿有记。呜呼。伯玉草野一书生也。在身在家在乡在国在天下。将多其所载。而大其所覆者耶。是未可知也。顾健于当健。顺于当顺。一其生生。以长以厚。随其所及。尽其所载。尚无负天地之所与。
厚。伯玉愿有记。呜呼。伯玉草野一书生也。在身在家在乡在国在天下。将多其所载。而大其所覆者耶。是未可知也。顾健于当健。顺于当顺。一其生生。以长以厚。随其所及。尽其所载。尚无负天地之所与。万石亭记
雪岳皆石也。岳之馀据海亦皆石也。有冒薄土。有涵积水。姑置其不见于外者。即其硉兀乎云宵。埼礒乎风涛。而数之不知其几大万也。岳东海西。有李运一之亭。以万石名而要余记。余意其取之于岳与海也。乃运一则指其篱边之碌碌。溪傍之硁硁而曰。此吾所取之万石也。始余
霅桥集卷四 第 508H 页
 倍而有馀。昆崙为白头之祖。而浑山玉石。其高二千五百里。则又非白头之伦矣。汉挐则是岳之孙。而石之出海方三百里。其标之高四十里。与是东澨之峙者何如哉。然皆见包于天地。藐乎不胜其小也。则奚异于在是亭者之于在是岳是海者乎。抑亭之累累。较之岳麓之腐壤。海滨之飞沙。亦为在岳者之昆崙。在海者之汉挐。何遽不足以自大乎。是知大小判于相形。而抑扬由于所向。于其大而求其小。抑而小之可也。于其小而求其大。扬而大之可也。噫。物情固然。亦非戏之也。遂莞尔而笑曰。运一乎。子之名亭。良有以也。当为子记之。运一亦笑曰。是偶然也。非有以也。将记之而更提运一曰。于是焉谓之有以可也。归之偶然亦可也。不必屑屑而竟之。抑子之字运一。亭之号万石。万石而运以一。其将用之者乎。是则必非偶然也。顾用之将若何。鍊之而供补天之具耶。升之河汉而支织女之机耶。作之砺乎殷宗之金耶。自他山而攻雅人之玉耶。渤海驾桥。当避羸氏之鞭耶。鱼腹之浦。或排孔明之八阵耶。值朱勔而充艮岳之贡耶。与雍伯而为玉田之种耶。郁林镇陆续之舟耶。菱溪贲刘金之宅耶。展之栗里而卧元亮之醉耶。输之平
倍而有馀。昆崙为白头之祖。而浑山玉石。其高二千五百里。则又非白头之伦矣。汉挐则是岳之孙。而石之出海方三百里。其标之高四十里。与是东澨之峙者何如哉。然皆见包于天地。藐乎不胜其小也。则奚异于在是亭者之于在是岳是海者乎。抑亭之累累。较之岳麓之腐壤。海滨之飞沙。亦为在岳者之昆崙。在海者之汉挐。何遽不足以自大乎。是知大小判于相形。而抑扬由于所向。于其大而求其小。抑而小之可也。于其小而求其大。扬而大之可也。噫。物情固然。亦非戏之也。遂莞尔而笑曰。运一乎。子之名亭。良有以也。当为子记之。运一亦笑曰。是偶然也。非有以也。将记之而更提运一曰。于是焉谓之有以可也。归之偶然亦可也。不必屑屑而竟之。抑子之字运一。亭之号万石。万石而运以一。其将用之者乎。是则必非偶然也。顾用之将若何。鍊之而供补天之具耶。升之河汉而支织女之机耶。作之砺乎殷宗之金耶。自他山而攻雅人之玉耶。渤海驾桥。当避羸氏之鞭耶。鱼腹之浦。或排孔明之八阵耶。值朱勔而充艮岳之贡耶。与雍伯而为玉田之种耶。郁林镇陆续之舟耶。菱溪贲刘金之宅耶。展之栗里而卧元亮之醉耶。输之平霅桥集卷四 第 508L 页
 泉而枕文饶之醒耶。神镂天划于清士之袖耶。豹首虎鼻于高僧之盆耶。谚曰。草不见木之长。木不见石之长。使是石可长而绰绰于用。则吾为子愿之者。在乎鼓之歧阳而纪宗周中兴之绩。碣之燕然而铭大汉北伐之功矣。呜呼。子其谓之何。运一曰善。请书之为记。
泉而枕文饶之醒耶。神镂天划于清士之袖耶。豹首虎鼻于高僧之盆耶。谚曰。草不见木之长。木不见石之长。使是石可长而绰绰于用。则吾为子愿之者。在乎鼓之歧阳而纪宗周中兴之绩。碣之燕然而铭大汉北伐之功矣。呜呼。子其谓之何。运一曰善。请书之为记。三清堂记
余族孙春老。于砥山之初川。名所居曰三清之堂。要余记。问其取名之义。曰月之白而风则清也。山之高而水则清也。茶之熟而香则清也。余曰。不亦善乎。风月而受天之清。山水而有地之清。茶香而在人之清也。即一堂而三才之美具矣。抑子之取美也。其将止于此而已乎。将约而求之于一身而备三才之清乎。将推而广之。以清一世而毕三才之治乎。三元二十八宿。使之华润而销落旄头之芒。则普天而斯清矣。五岳四渎。使之明秀而刮磨狼望之尘。则博地而斯清矣。礼乐九州。会同万国。而刳剔腥臊。涤荡污染。则是清一世之人也。子其能有志于此乎。果有志于此。则盍先清之于身乎。心气清明则清吾之天也。形体静洁则清吾之地也。光粹其言行而人事则清矣。一
霅桥集卷四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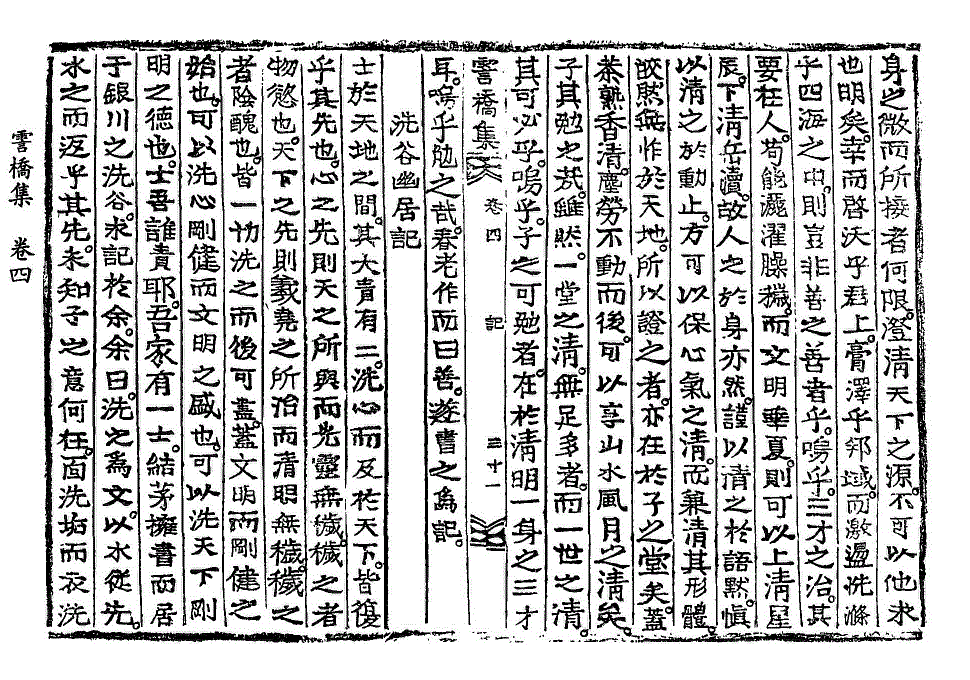 身之微而所接者何限。澄清天下之源。不可以他求也明矣。幸而启沃乎君上。膏泽乎邦域。而激荡洗涤乎四海之中。则岂非善之善者乎。呜乎。三才之治。其要在人。苟能洒濯臊秽。而文明华夏。则可以上清星辰。下清岳渎。故人之于身亦然。谨以清之于语默。慎以清之于动止。方可以保心气之清。而兼清其形体。皎然无怍于天地。所以證之者。亦在于子之堂矣。盖茶熟香清。尘劳不动而后。可以享山水风月之清矣。子其勉之哉。虽然。一堂之清。无足多者。而一世之清。其可必乎。呜乎。子之可勉者。在于清明一身之三才耳。呜乎勉之哉。春老作而曰善。遂书之为记。
身之微而所接者何限。澄清天下之源。不可以他求也明矣。幸而启沃乎君上。膏泽乎邦域。而激荡洗涤乎四海之中。则岂非善之善者乎。呜乎。三才之治。其要在人。苟能洒濯臊秽。而文明华夏。则可以上清星辰。下清岳渎。故人之于身亦然。谨以清之于语默。慎以清之于动止。方可以保心气之清。而兼清其形体。皎然无怍于天地。所以證之者。亦在于子之堂矣。盖茶熟香清。尘劳不动而后。可以享山水风月之清矣。子其勉之哉。虽然。一堂之清。无足多者。而一世之清。其可必乎。呜乎。子之可勉者。在于清明一身之三才耳。呜乎勉之哉。春老作而曰善。遂书之为记。洗谷幽居记
士于天地之间。其大青有二。洗心而及于天下。皆复乎其先也。心之先则天之所与而光灵无秽。秽之者物欲也。天下之先则羲尧之所治而清明无秽。秽之者阴丑也。皆一切洗之而后可尽。盖文明而刚健之始也。可以洗心刚健而文明之盛也。可以洗天下刚明之德也。士吾谁责耶。吾家有一士。结茅拥书而居于银川之洗谷。求记于余。余曰。洗之为文。以水从先。水之而返乎其先。未知子之意何在。面洗垢而衣洗
霅桥集卷四 第 509L 页
 尘。四民之所同也。非可以为士之大责。倘其在于洗心乎。在于洗天下乎。面对于人。而心与天相对。衣在身之外。而天下不外于心。则此其内外大小之轻重判矣。如使此心秽之在先。而未尝光灵。则何必洗之乎。使天下秽之在先。而未尝清明。则亦何必洗之乎。呜呼。天之与仁义而为和平四海之具。湛如止水。赫如日月者。惜其为物欲之所秽。故责夫士通理持敬而洗之。昊羲尧舜之叙彝伦兴礼乐而布法制。焕乎经天而纬地者。痛其为阴丑之所秽。故责夫士相君行道而洗之。王履癸尝秽尧舜之天下矣。伊尹佐成汤而洗之。帝辛尝秽成汤之天下矣。周公赞武王而洗之。周以下一秽一洗。不可遽数。而至于铁木之胡。而秽之太甚矣。大明之赫然洗之也。刘基徐达左右我 高皇帝。人文之盛。希商周而慕尧舜。融朗三百年。今为黑水之戎所秽。噫其痛矣。华夏不可久输于沙漠。衣冠不可久掩于毡裘。彝伦不可久坏于冒没轻儳。礼乐不可久散于驰蹂射猎。洒扫之濯磨之。以还我明之天下。是其责必有所归矣。子之屹然正坐。读天下书。将以何为者也。翼我 圣王。广提英杰。倾东海而洗中州。宁非子之责欤。抑其源在于子之心。
尘。四民之所同也。非可以为士之大责。倘其在于洗心乎。在于洗天下乎。面对于人。而心与天相对。衣在身之外。而天下不外于心。则此其内外大小之轻重判矣。如使此心秽之在先。而未尝光灵。则何必洗之乎。使天下秽之在先。而未尝清明。则亦何必洗之乎。呜呼。天之与仁义而为和平四海之具。湛如止水。赫如日月者。惜其为物欲之所秽。故责夫士通理持敬而洗之。昊羲尧舜之叙彝伦兴礼乐而布法制。焕乎经天而纬地者。痛其为阴丑之所秽。故责夫士相君行道而洗之。王履癸尝秽尧舜之天下矣。伊尹佐成汤而洗之。帝辛尝秽成汤之天下矣。周公赞武王而洗之。周以下一秽一洗。不可遽数。而至于铁木之胡。而秽之太甚矣。大明之赫然洗之也。刘基徐达左右我 高皇帝。人文之盛。希商周而慕尧舜。融朗三百年。今为黑水之戎所秽。噫其痛矣。华夏不可久输于沙漠。衣冠不可久掩于毡裘。彝伦不可久坏于冒没轻儳。礼乐不可久散于驰蹂射猎。洒扫之濯磨之。以还我明之天下。是其责必有所归矣。子之屹然正坐。读天下书。将以何为者也。翼我 圣王。广提英杰。倾东海而洗中州。宁非子之责欤。抑其源在于子之心。霅桥集卷四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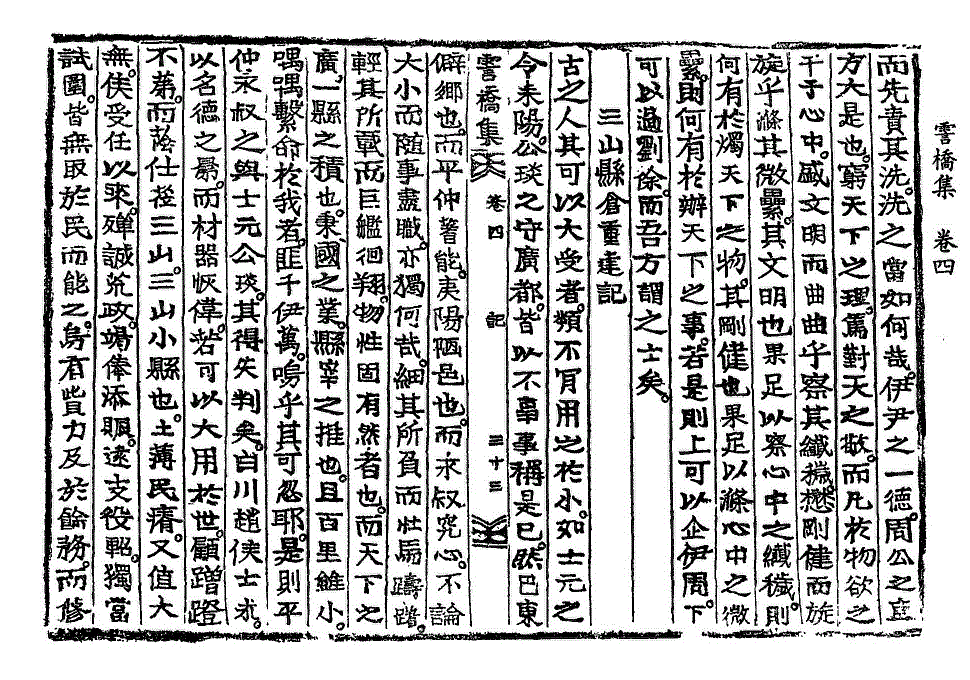 而先责其洗。洗之当如何哉。伊尹之一德。周公之直方大是也。穷天下之理。笃对天之敬。而凡于物欲之干子心中。盛文明而曲曲乎察其纤秽。懋刚健而旋旋乎涤其微累。其文明也果足以察心中之纤秽。则何有于烛天下之物。其刚健也果足以涤心中之微累。则何有于办天下之事。若是则上可以企伊周。下可以过刘徐。而吾方谓之士矣。
而先责其洗。洗之当如何哉。伊尹之一德。周公之直方大是也。穷天下之理。笃对天之敬。而凡于物欲之干子心中。盛文明而曲曲乎察其纤秽。懋刚健而旋旋乎涤其微累。其文明也果足以察心中之纤秽。则何有于烛天下之物。其刚健也果足以涤心中之微累。则何有于办天下之事。若是则上可以企伊周。下可以过刘徐。而吾方谓之士矣。三山县仓重建记
古之人其可以大受者。类不肯用之于小。如士元之令耒阳。公琰之守广都。皆以不事事称是已。然巴东僻乡也。而平仲著能。夷阳陋邑也。而永叔究心。不论大小而随事尽职。亦独何哉。细其所负而壮马踌躇。轻其所载而巨舰徊翔。物性固有然者也。而天下之广。一县之积也。秉国之业。县宰之推也。且百里虽小。喁喁系命于我者。匪千伊万。呜乎其可忽耶。是则平仲永叔之与士元公琰。其得失判矣。白川赵侯士求。以名德之昆。而材器恢伟。若可以大用于世。顾蹭蹬不第。而荫仕莅三山。三山小县也。土薄民瘠。又值大无。侯受任以来。殚诚荒政。竭俸添赈。远支役轺。独当试围。皆无取于民而能之。乌有赀力及于馀务。而修
霅桥集卷四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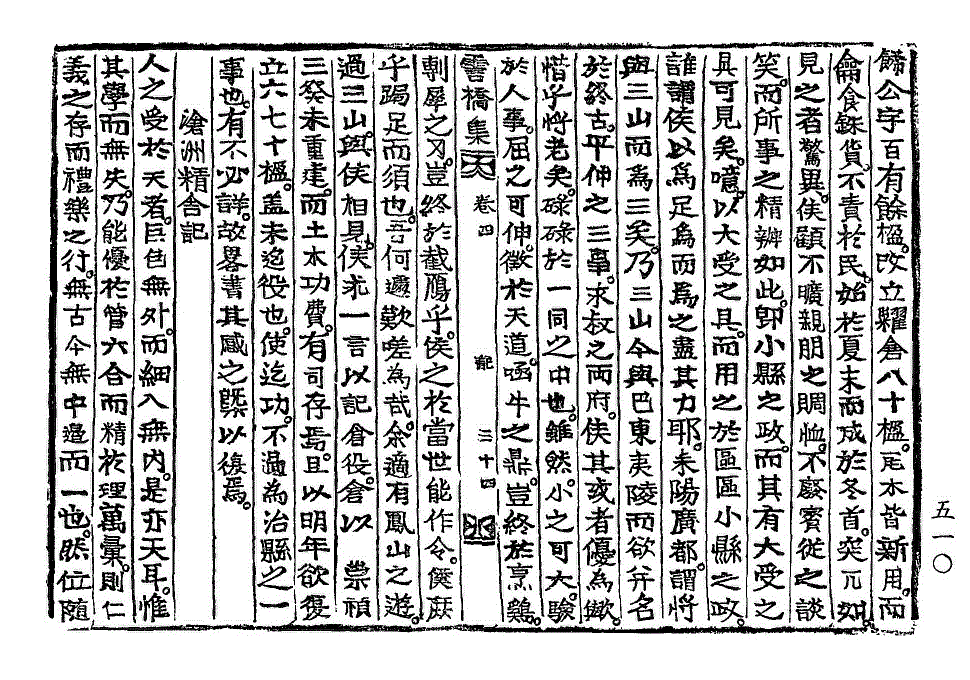 饰公宇百有馀楹。改立粜仓八十楹。瓦木皆新用。而龠食铢货。不责于民。始于夏末而成于冬首。突兀如。见之者惊异。侯顾不旷亲朋之赒恤。不废宾从之谈笑。而所事之精办如此。即小县之政。而其有大受之具可见矣。噫。以大受之具。而用之于区区小县之政。谁谓侯以为足为而为之尽其力耶。耒阳广都。谓将与三山而为三矣。乃三山今与巴东夷陵而欲并名于终古。平仲之三事。永叔之两府。侯其或者优为欤。惜乎将老矣。碌碌于一同之中也。虽然。小之可大。验于人事。屈之可伸。徵于天道。㖤牛之鼎。岂终于烹鸡。剸犀之刃。岂终于截雁乎。侯之于当世能作令。仆庶乎跼足而须也。吾何遽叹嗟为哉。余适有凤山之游。过三山。与侯相见。侯求一言以记仓役。仓以 崇祯三癸未重建。而土木功费。有司存焉。且以明年欲复立六七十楹。盖未迄役也。使迄功。不过为治县之一事也。有不必详。故略书其感之槩以复焉。
饰公宇百有馀楹。改立粜仓八十楹。瓦木皆新用。而龠食铢货。不责于民。始于夏末而成于冬首。突兀如。见之者惊异。侯顾不旷亲朋之赒恤。不废宾从之谈笑。而所事之精办如此。即小县之政。而其有大受之具可见矣。噫。以大受之具。而用之于区区小县之政。谁谓侯以为足为而为之尽其力耶。耒阳广都。谓将与三山而为三矣。乃三山今与巴东夷陵而欲并名于终古。平仲之三事。永叔之两府。侯其或者优为欤。惜乎将老矣。碌碌于一同之中也。虽然。小之可大。验于人事。屈之可伸。徵于天道。㖤牛之鼎。岂终于烹鸡。剸犀之刃。岂终于截雁乎。侯之于当世能作令。仆庶乎跼足而须也。吾何遽叹嗟为哉。余适有凤山之游。过三山。与侯相见。侯求一言以记仓役。仓以 崇祯三癸未重建。而土木功费。有司存焉。且以明年欲复立六七十楹。盖未迄役也。使迄功。不过为治县之一事也。有不必详。故略书其感之槩以复焉。沧洲精舍记
人之受于天者。巨包无外。而细入无内。是亦天耳。惟其学而无失。乃能优于管六合而精于理万汇。则仁义之存而礼乐之行。无古今无中边而一也。然位随
霅桥集卷四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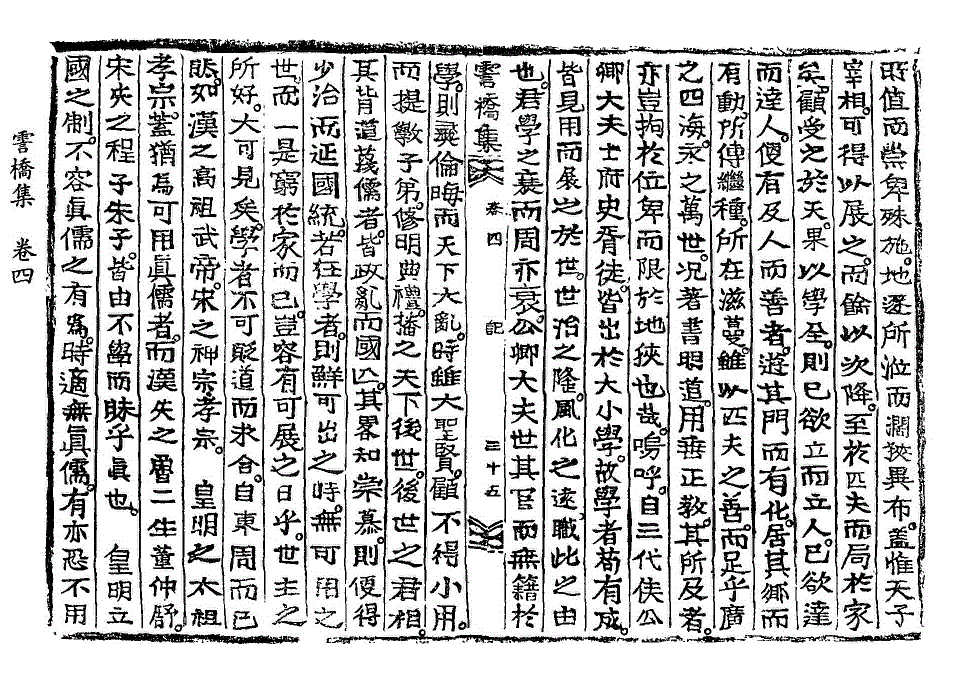 所值而崇卑殊施。地逐所涖而阔狭异布。盖惟天子宰相。可得以展之。而馀以次降。至于匹夫而局于家矣。顾受之于天。果以学全。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有及人而善者。游其门而有化。居其乡而有动。所传继种。所在滋蔓。虽以匹夫之善。而足乎广之四海。永之万世。况著书明道。用垂正教。其所及者。亦岂拘于位卑而限于地狭也哉。呜呼。自三代侯公卿大夫士府史胥徒。皆出于大小学。故学者苟有成。皆见用而展之于世。世治之隆。风化之远。职此之由也。君学之衰而周亦衰。公卿大夫世其官而无籍于学。则彝伦晦而天下大乱。时虽大圣贤。顾不得小用。而提敩子弟。修明典礼。播之天下后世。后世之君相。其背道蔑儒者。皆政乱而国亡。其略知崇慕。则便得少治而延国统。若在学者。则鲜可出之时。无可用之世。而一是穷于家而已。岂容有可展之日乎。世主之所好。大可见矣。学者不可贬道而求合。自东周而已然。如汉之高祖武帝。宋之神宗,孝宗。 皇明之太祖孝宗。盖犹为可用真儒者。而汉失之鲁二生董仲舒。宋失之程子朱子。皆由不学而昧乎真也。 皇明立国之制。不容真儒之有为。时适无真儒。有亦恐不用
所值而崇卑殊施。地逐所涖而阔狭异布。盖惟天子宰相。可得以展之。而馀以次降。至于匹夫而局于家矣。顾受之于天。果以学全。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有及人而善者。游其门而有化。居其乡而有动。所传继种。所在滋蔓。虽以匹夫之善。而足乎广之四海。永之万世。况著书明道。用垂正教。其所及者。亦岂拘于位卑而限于地狭也哉。呜呼。自三代侯公卿大夫士府史胥徒。皆出于大小学。故学者苟有成。皆见用而展之于世。世治之隆。风化之远。职此之由也。君学之衰而周亦衰。公卿大夫世其官而无籍于学。则彝伦晦而天下大乱。时虽大圣贤。顾不得小用。而提敩子弟。修明典礼。播之天下后世。后世之君相。其背道蔑儒者。皆政乱而国亡。其略知崇慕。则便得少治而延国统。若在学者。则鲜可出之时。无可用之世。而一是穷于家而已。岂容有可展之日乎。世主之所好。大可见矣。学者不可贬道而求合。自东周而已然。如汉之高祖武帝。宋之神宗,孝宗。 皇明之太祖孝宗。盖犹为可用真儒者。而汉失之鲁二生董仲舒。宋失之程子朱子。皆由不学而昧乎真也。 皇明立国之制。不容真儒之有为。时适无真儒。有亦恐不用霅桥集卷四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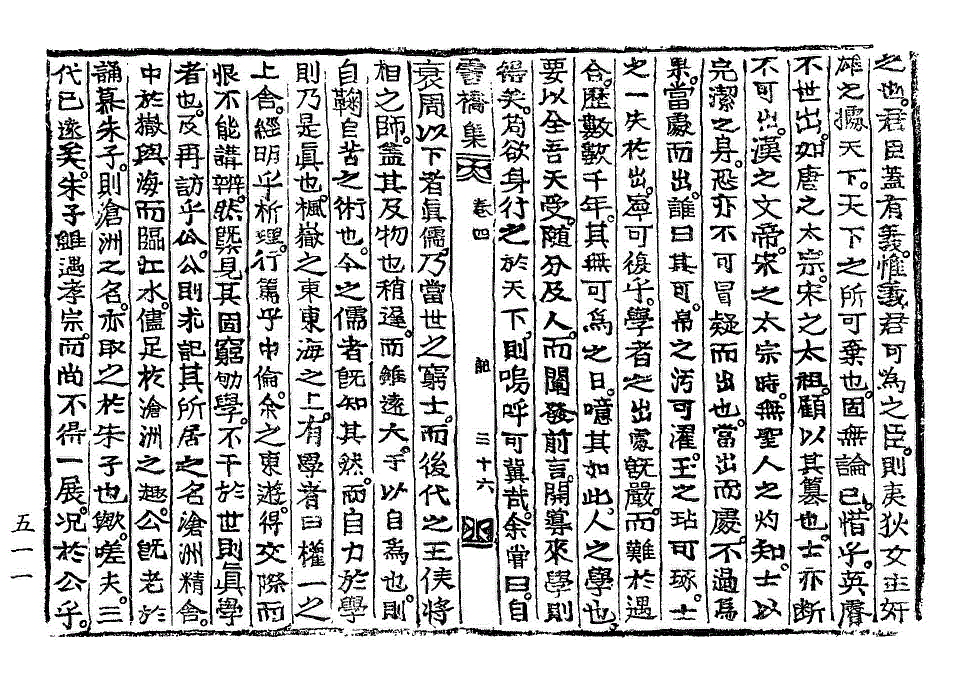 之也。君臣盖有义。惟义君可为之臣。则夷狄女主奸雄之据天下。天下之所可弃也。固无论已。惜乎。英睿不世出。知唐之太宗。宋之太祖。顾以其篡也。士亦断不可出。汉之文帝。宋之太宗时。无圣人之灼知。士以完洁之身。恐亦不可冒疑而出也。当出而处。不过为果。当处而出。谁曰其可。帛之污可濯。玉之玷可琢。士之一失于出。宁可复乎。学者之出处既严。而难于遇合。历数数千年。其无可为之日。噫其如此。人之学也。要以全吾天受。随分及人。而阐发前言。开导来学则得矣。苟欲身行之于天下。则呜呼可冀哉。余尝曰。自衰周以下者真儒。乃当世之穷士。而后代之王侯将相之师。盖其及物也稍迟。而虽远大。于以自为也。则自鞠自苦之术也。今之儒者既知其然。而自力于学则乃是真也。枫岳之东东海之上。有学者曰权一之上舍。经明乎析理。行笃乎中伦。余之东游。得交际而恨不能讲辨。然槩见其固穷劬学。不干于世则真学者也。及再访乎公。公则求记其所居之名沧洲精舍。中于岳与海而临江水。尽足于沧洲之趣。公既老于诵慕朱子。则沧洲之名。亦取之于朱子也欤。嗟夫。三代已远矣。朱子虽遇孝宗。而尚不得一展。况于公乎。
之也。君臣盖有义。惟义君可为之臣。则夷狄女主奸雄之据天下。天下之所可弃也。固无论已。惜乎。英睿不世出。知唐之太宗。宋之太祖。顾以其篡也。士亦断不可出。汉之文帝。宋之太宗时。无圣人之灼知。士以完洁之身。恐亦不可冒疑而出也。当出而处。不过为果。当处而出。谁曰其可。帛之污可濯。玉之玷可琢。士之一失于出。宁可复乎。学者之出处既严。而难于遇合。历数数千年。其无可为之日。噫其如此。人之学也。要以全吾天受。随分及人。而阐发前言。开导来学则得矣。苟欲身行之于天下。则呜呼可冀哉。余尝曰。自衰周以下者真儒。乃当世之穷士。而后代之王侯将相之师。盖其及物也稍迟。而虽远大。于以自为也。则自鞠自苦之术也。今之儒者既知其然。而自力于学则乃是真也。枫岳之东东海之上。有学者曰权一之上舍。经明乎析理。行笃乎中伦。余之东游。得交际而恨不能讲辨。然槩见其固穷劬学。不干于世则真学者也。及再访乎公。公则求记其所居之名沧洲精舍。中于岳与海而临江水。尽足于沧洲之趣。公既老于诵慕朱子。则沧洲之名。亦取之于朱子也欤。嗟夫。三代已远矣。朱子虽遇孝宗。而尚不得一展。况于公乎。霅桥集卷四 第 512H 页
 所可冀者。独有自进其学。以全其天。而教诲蒙𥠧。感化遐僻。勤于著述。以待千载而已。朱子尝释圣贤之书。择群儒之言。焕乎有编集。昭乎开后人之心目。而我东儒贤平实之语。精眇之论。公亦有意于抡采编定。而藏之深山。传之多士。吁其盛矣。海岳之奇。而余每恨其不足于游。游公尤为不足。耕获有暇。将复东之。钓鲢撷芝。从公于精舍。讲朱子遗编。辨公所编东儒之说。庶乎开吾知而全吾天判。与公老于穷海。于时欲干字。托之楣间。而公遽飞书五百里申索之。玆以略书勉学全天违世立言之故。投示及公之门者。抑公已知之矣。何俟乎斯语。
所可冀者。独有自进其学。以全其天。而教诲蒙𥠧。感化遐僻。勤于著述。以待千载而已。朱子尝释圣贤之书。择群儒之言。焕乎有编集。昭乎开后人之心目。而我东儒贤平实之语。精眇之论。公亦有意于抡采编定。而藏之深山。传之多士。吁其盛矣。海岳之奇。而余每恨其不足于游。游公尤为不足。耕获有暇。将复东之。钓鲢撷芝。从公于精舍。讲朱子遗编。辨公所编东儒之说。庶乎开吾知而全吾天判。与公老于穷海。于时欲干字。托之楣间。而公遽飞书五百里申索之。玆以略书勉学全天违世立言之故。投示及公之门者。抑公已知之矣。何俟乎斯语。乐生轩记
清风金伯高鸿儒也。以世胄而辞京第。野居于广州。与其弟定夫。讲书折义。不舍晨夕。间者名其轩以乐生。求记于余。余问其取名之故。伯高曰。我金氏始也。畸穷而力学起家。实自于广州之野。今以藐然余兄弟。虽在显严之位。而惟先古之穷居力学。不敢不慕。居必于其居。学必于其学。礼不云乎。乐乐其所自生。此吾轩名之所取也。余不觉喟然而叹曰。贤哉子乎。世亦华胄而能如子之为者有几。子固已深于学。而
霅桥集卷四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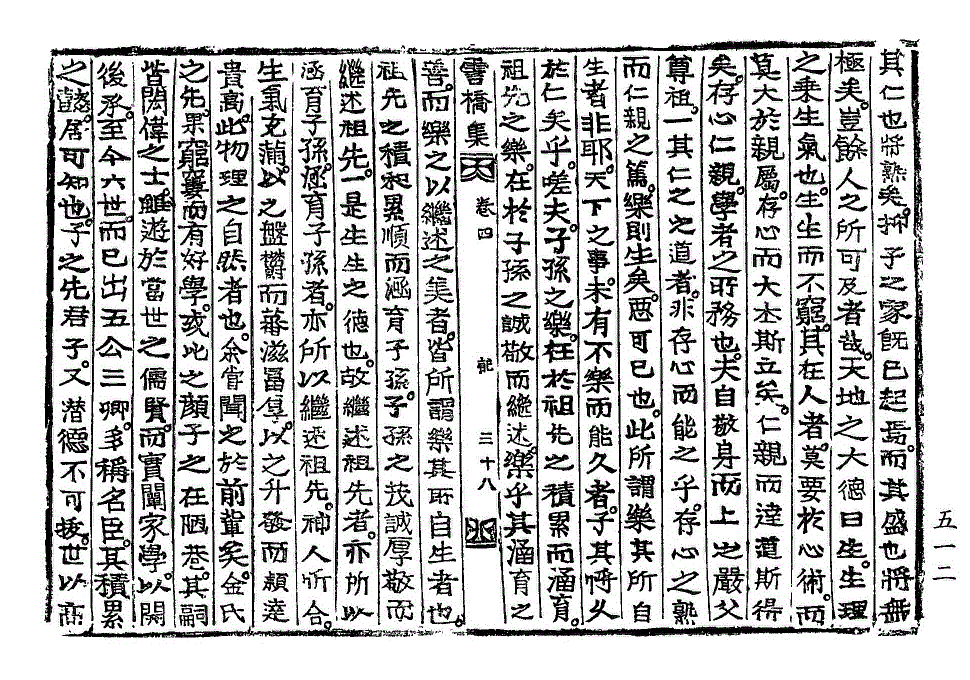 其仁也将熟矣。抑子之家既已起焉。而其盛也将无极矣。岂馀人之所可及者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之乘生气也。生生而不穷。其在人者。莫要于心术。而莫大于亲属。存心而大本斯立矣。仁亲而达道斯得矣。存心仁亲。学者之所务也。夫自敬身而上之严父尊祖。一其仁之之道者。非存心而能之乎。存心之熟而仁亲之笃。乐则生矣。恶可已也。此所谓乐其所自生者非耶。天下之事。未有不乐而能久者。子其将久于仁矣乎。嗟夫。子孙之乐。在于祖先之积累而涵育。祖先之乐。在于子孙之诚敬而继述。乐乎其涵育之善。而乐之以继述之美者。皆所谓乐其所自生者也。祖先之积和累顺而涵育子孙。子孙之茂诚厚敬而继述祖先。一是生生之德也。故继述祖先者。亦所以涵育子孙。涵育子孙者。亦所以继述祖先。神人忻合。生气充满。以之盘郁而蕃滋富厚。以之升发而颖达贵高。此物理之自然者也。余尝闻之于前辈矣。金氏之先。果穷窭而有好学。或比之颜子之在陋巷。其嗣皆闳伟之士。虽游于当世之儒贤。而实阐家学。以开后承。至今六世。而已出五公三卿。多称名臣。其积累之懿。居可知也。子之先君子。又潜德不可拔。世以高
其仁也将熟矣。抑子之家既已起焉。而其盛也将无极矣。岂馀人之所可及者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之乘生气也。生生而不穷。其在人者。莫要于心术。而莫大于亲属。存心而大本斯立矣。仁亲而达道斯得矣。存心仁亲。学者之所务也。夫自敬身而上之严父尊祖。一其仁之之道者。非存心而能之乎。存心之熟而仁亲之笃。乐则生矣。恶可已也。此所谓乐其所自生者非耶。天下之事。未有不乐而能久者。子其将久于仁矣乎。嗟夫。子孙之乐。在于祖先之积累而涵育。祖先之乐。在于子孙之诚敬而继述。乐乎其涵育之善。而乐之以继述之美者。皆所谓乐其所自生者也。祖先之积和累顺而涵育子孙。子孙之茂诚厚敬而继述祖先。一是生生之德也。故继述祖先者。亦所以涵育子孙。涵育子孙者。亦所以继述祖先。神人忻合。生气充满。以之盘郁而蕃滋富厚。以之升发而颖达贵高。此物理之自然者也。余尝闻之于前辈矣。金氏之先。果穷窭而有好学。或比之颜子之在陋巷。其嗣皆闳伟之士。虽游于当世之儒贤。而实阐家学。以开后承。至今六世。而已出五公三卿。多称名臣。其积累之懿。居可知也。子之先君子。又潜德不可拔。世以高霅桥集卷四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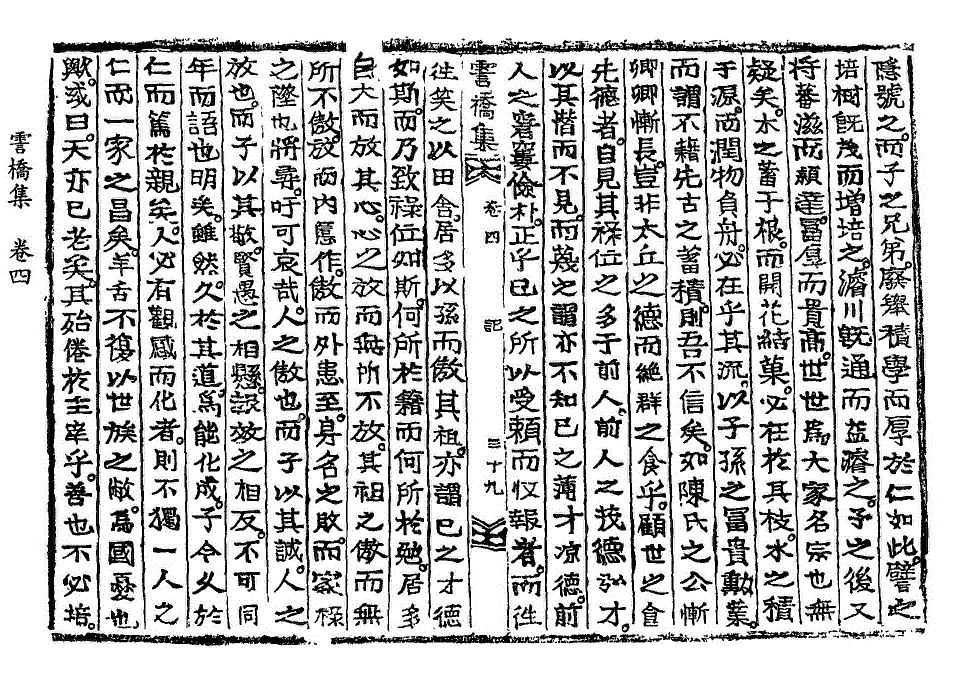 隐号之。而子之兄弟。废举积学而厚于仁如此。譬之培树既茂而增培之。浚川既通而益浚之。子之后又将蕃滋而颖达。富厚而贵高。世世为大家名宗也无疑矣。木之蓄于根。而开花结果。必在于其枝。水之积于源。而润物负舟。必在乎其流。以子孙之富贵勋业。而谓不藉先古之蓄积。则吾不信矣。如陈氏之公惭卿卿惭长。岂非太丘之德而绝群之食乎。顾世之食先德者。自见其禄位之多于前人。前人之茂德弘才。以其潜而不见。而蔑之谓亦不知己之薄才凉德。前人之窘窭俭朴。正乎己之所以受赖而收报者。而往往笑之以田舍。居多以孙而傲其祖。亦谓己之才德如斯。而乃致禄位如斯。何所于籍而何所于勉。居多自大而放其心。心之放而无所不放。其祖之傲而无所不傲。放而内慝作。傲而外患至。身名之败。而家禄之坠也将寻。吁可哀哉。人之傲也。而子以其诚。人之放也。而子以其敬。贤愚之相悬。报效之相反。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虽然。久于其道。为能化成。子今久于仁而笃于亲矣。人必有观感而化者。则不独一人之仁而一家之昌矣。羊舌不复以世族之敝。为国忧也欤。或曰。天亦已老矣。其殆倦于主宰乎。善也不必培。
隐号之。而子之兄弟。废举积学而厚于仁如此。譬之培树既茂而增培之。浚川既通而益浚之。子之后又将蕃滋而颖达。富厚而贵高。世世为大家名宗也无疑矣。木之蓄于根。而开花结果。必在于其枝。水之积于源。而润物负舟。必在乎其流。以子孙之富贵勋业。而谓不藉先古之蓄积。则吾不信矣。如陈氏之公惭卿卿惭长。岂非太丘之德而绝群之食乎。顾世之食先德者。自见其禄位之多于前人。前人之茂德弘才。以其潜而不见。而蔑之谓亦不知己之薄才凉德。前人之窘窭俭朴。正乎己之所以受赖而收报者。而往往笑之以田舍。居多以孙而傲其祖。亦谓己之才德如斯。而乃致禄位如斯。何所于籍而何所于勉。居多自大而放其心。心之放而无所不放。其祖之傲而无所不傲。放而内慝作。傲而外患至。身名之败。而家禄之坠也将寻。吁可哀哉。人之傲也。而子以其诚。人之放也。而子以其敬。贤愚之相悬。报效之相反。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虽然。久于其道。为能化成。子今久于仁而笃于亲矣。人必有观感而化者。则不独一人之仁而一家之昌矣。羊舌不复以世族之敝。为国忧也欤。或曰。天亦已老矣。其殆倦于主宰乎。善也不必培。霅桥集卷四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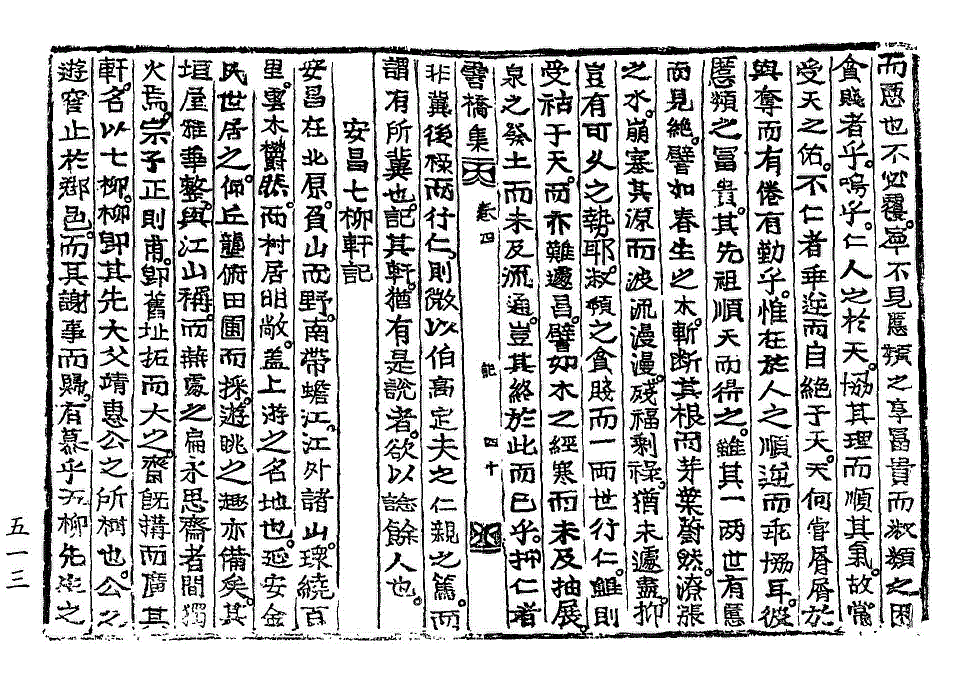 而恶也不必覆。宁不见慝类之享富贵而淑类之困贫贱者乎。呜乎。仁人之于天。协其理而顺其气。故常受天之佑。不仁者乖逆而自绝于天。天何尝屑屑于与夺而有倦有勤乎。惟在于人之顺逆而乖协耳。彼慝类之富贵。其先祖顺天而得之。虽其一两世有慝而见绝。譬如春生之木。斩断其根而芽叶蔚然。潦涨之水。崩塞其源而波流漫漫。残福剩禄。犹未遽尽。抑岂有可久之势耶。淑类之贫贱而一两世行仁。虽则受祜于天。而亦难遽昌。譬如木之经寒而未及抽展。泉之发土而未及流通。岂其终于此而已乎。抑仁者非冀后禄而行仁。则微以伯高定夫之仁亲之笃。而谓有所冀也。记其轩。犹有是说者。欲以谂馀人也。
而恶也不必覆。宁不见慝类之享富贵而淑类之困贫贱者乎。呜乎。仁人之于天。协其理而顺其气。故常受天之佑。不仁者乖逆而自绝于天。天何尝屑屑于与夺而有倦有勤乎。惟在于人之顺逆而乖协耳。彼慝类之富贵。其先祖顺天而得之。虽其一两世有慝而见绝。譬如春生之木。斩断其根而芽叶蔚然。潦涨之水。崩塞其源而波流漫漫。残福剩禄。犹未遽尽。抑岂有可久之势耶。淑类之贫贱而一两世行仁。虽则受祜于天。而亦难遽昌。譬如木之经寒而未及抽展。泉之发土而未及流通。岂其终于此而已乎。抑仁者非冀后禄而行仁。则微以伯高定夫之仁亲之笃。而谓有所冀也。记其轩。犹有是说者。欲以谂馀人也。安昌七柳轩记
安昌在北原。负山而野。南带蟾江。江外诸山。环绕百里。云木郁然。而村居明敞。盖上游之名地也。延安金氏世居之。仰丘垄俯田圃而采。游眺之趣亦备矣。其垣屋雅华整。与江山称。而燕处之扁永思斋者间独火焉。宗子正则甫。即旧址拓而大之。斋既搆而广其轩。名以七柳。柳即其先大父靖惠公之所树也。公之游宦止于郡邑。而其谢事而归。有慕乎五柳先生之
霅桥集卷四 第 514H 页
 遗风也欤。余于弱冠。数尝陪游。而得见树柳之初矣。中岁屡拜都正公于此。而柳则渐长。映花坞而荫荷塘。盖已足于风流矣。是岁之夏访正则。正则酒之于轩中而求余记。余顾七柳皆成合抱。而黛色参山。爽气通江。而风枝演漾。散月明而动荷香矣。相与话旧而怅然。终夜不能眠。嗟乎。余之来往。居然三十馀年。而正则又冠子而抱孙矣。余固已白须。而见正则五世之颜面。今于是柳。自不觉摩抄而感叹也。人生亦何须勋名富贵。惟树德而殖学。以长子孙而世其家可矣。夫以靖惠公之茂德厚泽。都正公之克继无落。而游世不求于人。禄位未满其德。至于正则。亦仕退而不干进。务滋旧德而笃学崇礼。以教子而提孙。子孙皆礼秀和厚。蔼然有长发之气。譬之柳也。纯于木德。固易生而易长。由其深根而广抵也。枝干洪大。条叶峻茂。而正则方且培溉护养之不已。是其长大也荣茂也。吾将不知其所限矣。姑记之以俟。
遗风也欤。余于弱冠。数尝陪游。而得见树柳之初矣。中岁屡拜都正公于此。而柳则渐长。映花坞而荫荷塘。盖已足于风流矣。是岁之夏访正则。正则酒之于轩中而求余记。余顾七柳皆成合抱。而黛色参山。爽气通江。而风枝演漾。散月明而动荷香矣。相与话旧而怅然。终夜不能眠。嗟乎。余之来往。居然三十馀年。而正则又冠子而抱孙矣。余固已白须。而见正则五世之颜面。今于是柳。自不觉摩抄而感叹也。人生亦何须勋名富贵。惟树德而殖学。以长子孙而世其家可矣。夫以靖惠公之茂德厚泽。都正公之克继无落。而游世不求于人。禄位未满其德。至于正则。亦仕退而不干进。务滋旧德而笃学崇礼。以教子而提孙。子孙皆礼秀和厚。蔼然有长发之气。譬之柳也。纯于木德。固易生而易长。由其深根而广抵也。枝干洪大。条叶峻茂。而正则方且培溉护养之不已。是其长大也荣茂也。吾将不知其所限矣。姑记之以俟。乐隐庵记
余之入凤山也。与南先辈有诚甫隔峦而居。杖屦时相过。谈诗书话耕渔。荫茂林濯清渠。未尝不欣欣如也。有诚甫新搆小庵。名之以乐隐。使余记。余曰。子诚
霅桥集卷四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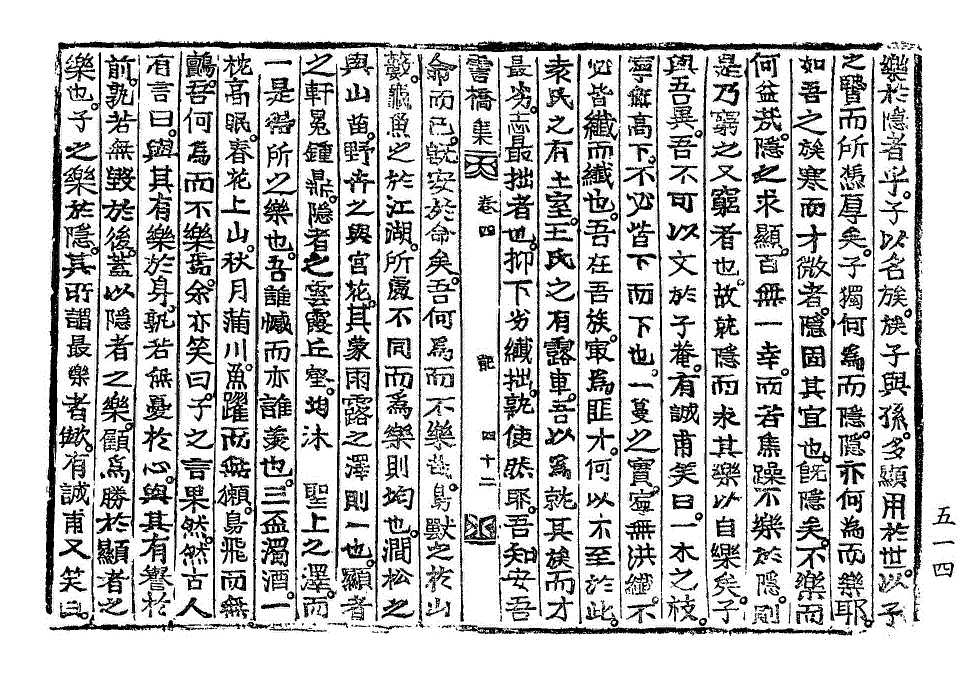 乐于隐者乎。子以名族。族子与孙。多显用于世。以子之贤而所凭厚矣。子独何为而隐。隐亦何为而乐耶。如吾之族寒而才微者。隐固其宜也。既隐矣。不乐而何益哉。隐之求显。百无一幸。而若焦躁不乐于隐。则是乃穷之又穷者也。故就隐而求其乐以自乐矣。子与吾异。吾不可以文于子庵。有诚甫笑曰。一木之枝。宁无高下。不必皆下而下也。一蔓之实。宁无洪纤。不必皆纤而纤也。吾在吾族。最为匪才。何以不至于此。袁氏之有土室。王氏之有露车。吾以为就其族而才最劣。志最拙者也。抑下劣纤拙。孰使然耶。吾知安吾命而已。既安于命矣。吾何为而不乐哉。鸟兽之于山薮。龟鱼之于江湖。所处不同而为乐则均也。涧松之与山苗。野卉之与宫花。其蒙雨露之泽则一也。显者之轩冕钟鼎。隐者之云霞丘壑。均沐 圣上之泽。而一是得所之乐也。吾谁戚而亦谁羡也。三杯浊酒。一枕高眠。春花上山。秋月满川。鱼跃而无獭。鸟飞而无鹯。吾何为而不乐焉。余亦笑曰。子之言果然。然古人有言曰。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盖以隐者之乐。顾为胜于显者之乐也。子之乐于隐。其所谓最乐者欤。有诚甫又笑曰。
乐于隐者乎。子以名族。族子与孙。多显用于世。以子之贤而所凭厚矣。子独何为而隐。隐亦何为而乐耶。如吾之族寒而才微者。隐固其宜也。既隐矣。不乐而何益哉。隐之求显。百无一幸。而若焦躁不乐于隐。则是乃穷之又穷者也。故就隐而求其乐以自乐矣。子与吾异。吾不可以文于子庵。有诚甫笑曰。一木之枝。宁无高下。不必皆下而下也。一蔓之实。宁无洪纤。不必皆纤而纤也。吾在吾族。最为匪才。何以不至于此。袁氏之有土室。王氏之有露车。吾以为就其族而才最劣。志最拙者也。抑下劣纤拙。孰使然耶。吾知安吾命而已。既安于命矣。吾何为而不乐哉。鸟兽之于山薮。龟鱼之于江湖。所处不同而为乐则均也。涧松之与山苗。野卉之与宫花。其蒙雨露之泽则一也。显者之轩冕钟鼎。隐者之云霞丘壑。均沐 圣上之泽。而一是得所之乐也。吾谁戚而亦谁羡也。三杯浊酒。一枕高眠。春花上山。秋月满川。鱼跃而无獭。鸟飞而无鹯。吾何为而不乐焉。余亦笑曰。子之言果然。然古人有言曰。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盖以隐者之乐。顾为胜于显者之乐也。子之乐于隐。其所谓最乐者欤。有诚甫又笑曰。霅桥集卷四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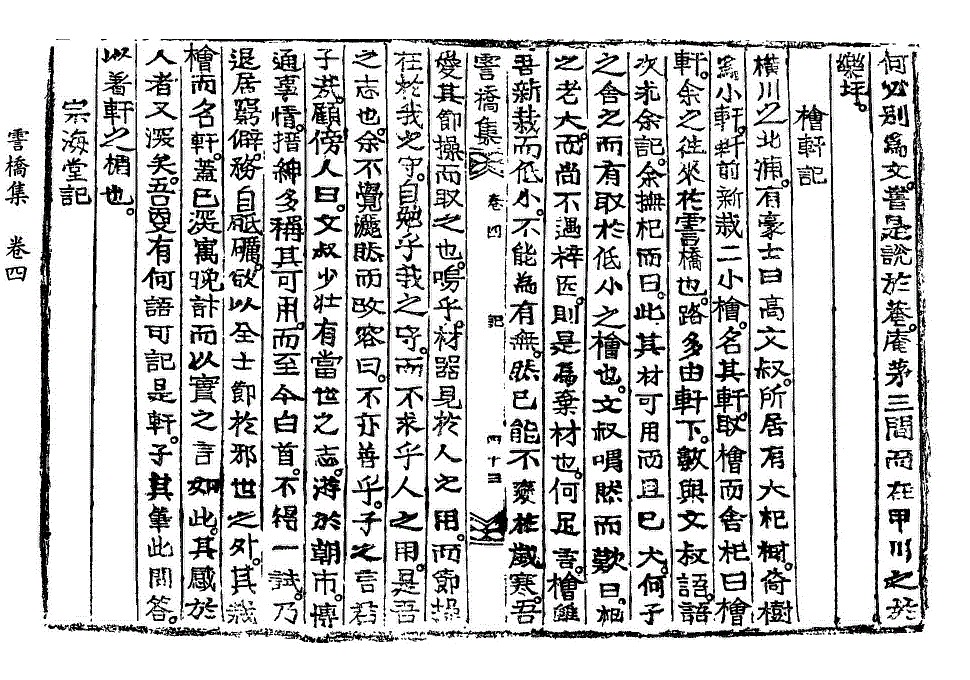 何必别为文。书是说于庵。庵茅三间而在甲川之于乐坪。
何必别为文。书是说于庵。庵茅三间而在甲川之于乐坪。桧轩记
横川之北浦。有豪士曰高文叔。所居有大杞树。倚树为小轩。轩前新栽二小桧。名其轩。取桧而舍杞曰桧轩。余之往来于霅桥也。路多由轩下。数与文叔语。语次求余记。余抚杞而曰。此其材可用而且已大。何子之舍之而有取于低小之桧也。文叔喟然而叹曰。杞之老大。而尚不遇梓匠。则是为弃材也。何足言。桧虽吾新栽而低小。不能为有无。然已能不变于岁寒。吾爱其节操而取之也。呜乎。材器见于人之用。而节操在于我之守。自勉乎我之守。而不求乎人之用。是吾之志也。余不觉洒然而改容曰。不亦善乎。子之言君子哉。顾傍人曰。文叔少壮有当世之志。游于朝市。博通事情。搢绅多称其可用。而至今白首。不得一试。乃退居穷僻。务自砥砺。欲以全士节于邪世之外。其栽桧而名轩。盖已深寓晚计而以实之言如此。其感于人者又深矣。吾更有何语可记是轩。子其笔此问答。以着轩之楣也。
宗海堂记
霅桥集卷四 第 515L 页
 余之游湖南也。访常山宋叔茂于高山之寒泉。谈讲之乐。至今未能忘也。盖临别。叔茂请记其宗海之堂。而略语其名之之义。后五年始记之而忘其语。独以江汉之朝宗。春秋之尊攘命乎。辞入递六年。方见其复书。曰子不记前日之语乎。东海宋先生。吾师也。先生以华阳老先生之玄孙。而世守春秋之义。隐遁不仕而不以天下为可忘。其以东海自号者。一取耻秦蹈东海之意也。一取避纣居东海之事也。吾师以豪杰之资。为圣贤之学。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中身弃世而道不传。以余之陋。遽失依归。伥伥乎无以自立。然不敢不勉。至白首孳孳。惟先生是慕。名吾堂宗海者。宗乎先生之东海也。子以是更记吾堂而董之也。余读之而叹曰。吾其为九方皋乎。天机之得而忘其骊黄矣。乃复之曰。一世林立之大儒。吾悦东海先生之风。而以及于子。一笑而莫逆于心者。独非朝宗之心尊攘之义乎。为我曝一腔热血。前记已泼之。更使吾何言哉。顾于太公鲁连之说。晚辈有疑之者曰。连之言曰秦即肆然而帝天下。连有蹈东海而死耳。盖连之不死。以秦之未及为帝也。彼虏之丑。百倍于秦。而帝天下百年。高士不死于海何哉。余曰。金吉甫许
余之游湖南也。访常山宋叔茂于高山之寒泉。谈讲之乐。至今未能忘也。盖临别。叔茂请记其宗海之堂。而略语其名之之义。后五年始记之而忘其语。独以江汉之朝宗。春秋之尊攘命乎。辞入递六年。方见其复书。曰子不记前日之语乎。东海宋先生。吾师也。先生以华阳老先生之玄孙。而世守春秋之义。隐遁不仕而不以天下为可忘。其以东海自号者。一取耻秦蹈东海之意也。一取避纣居东海之事也。吾师以豪杰之资。为圣贤之学。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中身弃世而道不传。以余之陋。遽失依归。伥伥乎无以自立。然不敢不勉。至白首孳孳。惟先生是慕。名吾堂宗海者。宗乎先生之东海也。子以是更记吾堂而董之也。余读之而叹曰。吾其为九方皋乎。天机之得而忘其骊黄矣。乃复之曰。一世林立之大儒。吾悦东海先生之风。而以及于子。一笑而莫逆于心者。独非朝宗之心尊攘之义乎。为我曝一腔热血。前记已泼之。更使吾何言哉。顾于太公鲁连之说。晚辈有疑之者曰。连之言曰秦即肆然而帝天下。连有蹈东海而死耳。盖连之不死。以秦之未及为帝也。彼虏之丑。百倍于秦。而帝天下百年。高士不死于海何哉。余曰。金吉甫许霅桥集卷四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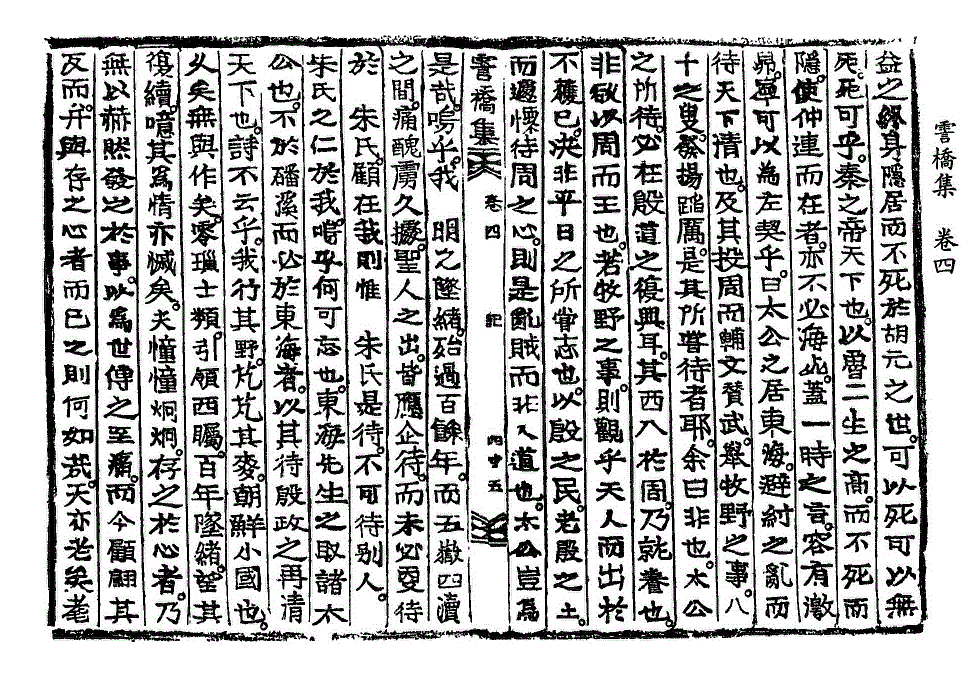 益之终身隐居而不死于胡元之世。可以死可以无庞。死可乎。秦之帝天下也。以鲁二生之高。而不死而隐。使仲连而在者。亦不必海死。盖一时之言。容有激昴。宁可以为左契乎。曰太公之居东海。避纣之乱而待天下清也。及其投周而辅文赞武。举牧野之事。八十之叟。发扬蹈厉。是其所尝待者耶。余曰非也。太公之所待。必在殷道之复兴耳。其西入于周。乃就养也。非欲以周而王也。若牧野之事。则观乎天人而出于不获已。决非平日之所尝志也。以殷之民。老殷之土。而遽怀待周之心。则是乱贼而非人道也。太公岂为是哉。呜乎。我 明之坠绪。殆过百馀年。而五岳四渎之间。痛丑虏久据。圣人之出。皆应企待。而未必更待于 朱氏。顾在我则惟 朱氏是待。不可待别人。 朱氏之仁于我。呜乎何可忘也。东海先生之取诸太公也。不于磻溪而必于东海者。以其待殷政之再清天下也。诗不云乎。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朝鲜小国也。久矣无与作矣。零琐士类。引领西瞩。百年坠绪。望其复续。噫其为情亦戚矣。夫憧憧炯炯。存之于心者。乃无以赫然发之于事。以为世传之至痛。而今顾翩其反而。并与存之心者而已之则何如哉。天亦老矣耄
益之终身隐居而不死于胡元之世。可以死可以无庞。死可乎。秦之帝天下也。以鲁二生之高。而不死而隐。使仲连而在者。亦不必海死。盖一时之言。容有激昴。宁可以为左契乎。曰太公之居东海。避纣之乱而待天下清也。及其投周而辅文赞武。举牧野之事。八十之叟。发扬蹈厉。是其所尝待者耶。余曰非也。太公之所待。必在殷道之复兴耳。其西入于周。乃就养也。非欲以周而王也。若牧野之事。则观乎天人而出于不获已。决非平日之所尝志也。以殷之民。老殷之土。而遽怀待周之心。则是乱贼而非人道也。太公岂为是哉。呜乎。我 明之坠绪。殆过百馀年。而五岳四渎之间。痛丑虏久据。圣人之出。皆应企待。而未必更待于 朱氏。顾在我则惟 朱氏是待。不可待别人。 朱氏之仁于我。呜乎何可忘也。东海先生之取诸太公也。不于磻溪而必于东海者。以其待殷政之再清天下也。诗不云乎。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朝鲜小国也。久矣无与作矣。零琐士类。引领西瞩。百年坠绪。望其复续。噫其为情亦戚矣。夫憧憧炯炯。存之于心者。乃无以赫然发之于事。以为世传之至痛。而今顾翩其反而。并与存之心者而已之则何如哉。天亦老矣耄霅桥集卷四 第 516L 页
 矣。未必从民之愿。纵使从之。未必九有之违。而一隅之士是从。或者周民经秦而睹汉。唐人阅五季而觌宋。则其久隐而自洁者。宁有仍废之义乎。虽然。汉未起而待汉忘周。宋未兴而待宋谖唐则有不忍也。以东海先生之义精仁笃。而必有以告于叔茂。叔茂之宗之也。岂徒然哉。疑而问之者洒然而对曰。真矣至矣大矣。小子亦欲宗宗海先生。而遂宗乎东海先生。余笑曰。河伯始知海若之为大方家乎。谨玆记其说以进之。便是更为记也。抑可以挂之檐楣之间欤。
矣。未必从民之愿。纵使从之。未必九有之违。而一隅之士是从。或者周民经秦而睹汉。唐人阅五季而觌宋。则其久隐而自洁者。宁有仍废之义乎。虽然。汉未起而待汉忘周。宋未兴而待宋谖唐则有不忍也。以东海先生之义精仁笃。而必有以告于叔茂。叔茂之宗之也。岂徒然哉。疑而问之者洒然而对曰。真矣至矣大矣。小子亦欲宗宗海先生。而遂宗乎东海先生。余笑曰。河伯始知海若之为大方家乎。谨玆记其说以进之。便是更为记也。抑可以挂之檐楣之间欤。崇祯三辛卯阳月甲午。顺兴后学安锡儆书。
独笑堂记
独笑翁临沧浪之水而老于家。琴书自娱。不与世往还。见之将三十年。而能一于澹然。盖有道者也。间指其堂独笑之篇而责记于余。余笑曰。独笑笑何事。岂人世之笑耶。翁亦笑曰。吾不耳目于世。何知何人之为可笑。笑故无所施。所尝目者。乃于水中之鱼而笑其可笑耳。余曰。鱼之可笑者何如哉。翁笑曰。凡物受气于天。受形于地。故所以养其形气者。不待他求。而即所在皆足。鱼之深潜。食其沉泥。亦可以生矣。何必闯觜闪尾。求食于近人之渚耶。吾是之笑矣。身之有文。
霅桥集卷四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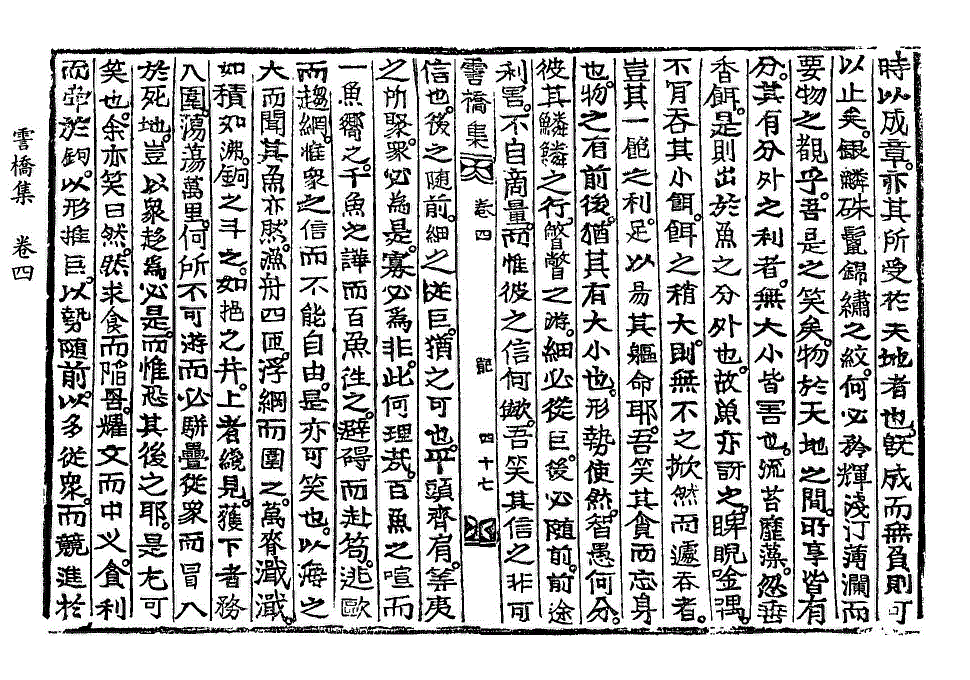 时以成章。亦其所受于天地者也。既成而无负则可以止矣。银鳞朱鬣锦绣之纹。何必矜辉浅汀薄澜而要物之睹乎。吾是之笑矣。物于天地之间。所享皆有分。其有分外之利者。无大小皆害也。流苔靡藻。忽垂香饵。是则出于鱼之分外也。故鱼亦讶之。睥睨唫喁。不肯吞其小饵。饵之稍大。则无不之掀然而遽吞者。岂其一饱之利。足以易其躯命耶。吾笑其贪而忘身也。物之有前后。犹其有大小也。形势使然。智愚何分。彼其鳞鳞之行。瞥瞥之游。细必从巨。后必随前。前途利害。不自商量。而惟彼之信何欤。吾笑其信之非可信也。后之随前。细之从巨。犹之可也。平头齐肩。算夷之所聚。众必为是。寡必为非。此何理哉。百鱼之喧而一鱼向之。千鱼之哗而百鱼往之。避碍而赴笱。逃欧而趋网。惟众之信而不能自由。是亦可笑也。以海之大而闻其鱼亦然。渔舟四匝。浮网而围之。万脊濈濈。如积如沸。钩之斗之。如挹之井。上者才见。获下者务入围。荡荡万里。何所不可游而必骈叠从众而冒入于死地。岂以众趍为必是。而惟恐其后之耶。是尤可笑也。余亦笑曰然。然求食而陷罟。耀文而中叉。贪利而牵于钩。以形推巨。以势随前。以多从众。而竞进于
时以成章。亦其所受于天地者也。既成而无负则可以止矣。银鳞朱鬣锦绣之纹。何必矜辉浅汀薄澜而要物之睹乎。吾是之笑矣。物于天地之间。所享皆有分。其有分外之利者。无大小皆害也。流苔靡藻。忽垂香饵。是则出于鱼之分外也。故鱼亦讶之。睥睨唫喁。不肯吞其小饵。饵之稍大。则无不之掀然而遽吞者。岂其一饱之利。足以易其躯命耶。吾笑其贪而忘身也。物之有前后。犹其有大小也。形势使然。智愚何分。彼其鳞鳞之行。瞥瞥之游。细必从巨。后必随前。前途利害。不自商量。而惟彼之信何欤。吾笑其信之非可信也。后之随前。细之从巨。犹之可也。平头齐肩。算夷之所聚。众必为是。寡必为非。此何理哉。百鱼之喧而一鱼向之。千鱼之哗而百鱼往之。避碍而赴笱。逃欧而趋网。惟众之信而不能自由。是亦可笑也。以海之大而闻其鱼亦然。渔舟四匝。浮网而围之。万脊濈濈。如积如沸。钩之斗之。如挹之井。上者才见。获下者务入围。荡荡万里。何所不可游而必骈叠从众而冒入于死地。岂以众趍为必是。而惟恐其后之耶。是尤可笑也。余亦笑曰然。然求食而陷罟。耀文而中叉。贪利而牵于钩。以形推巨。以势随前。以多从众。而竞进于霅桥集卷四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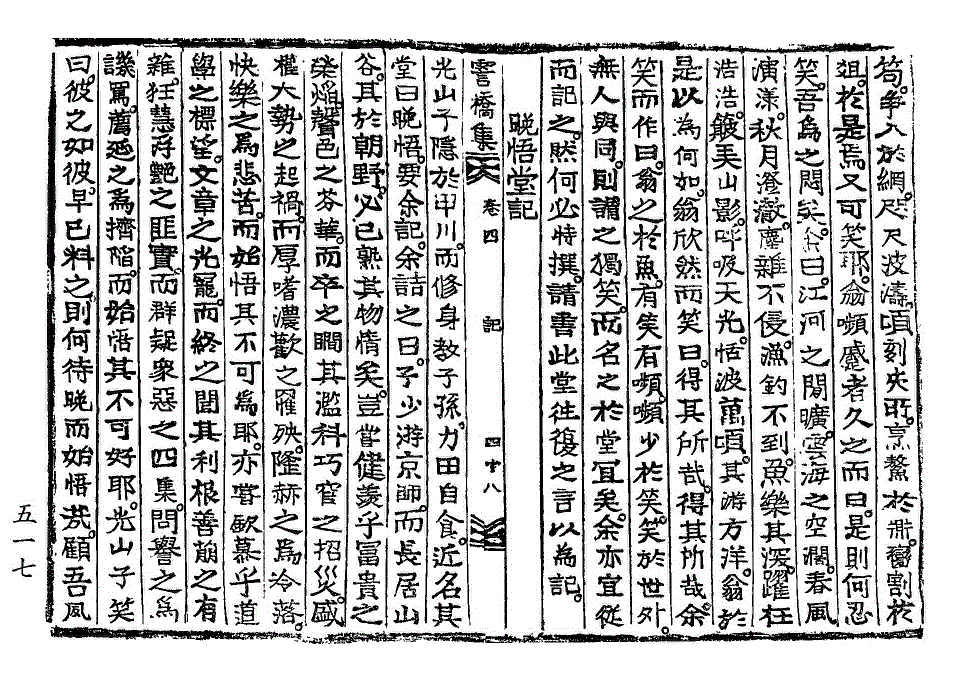 笱。争入于网。咫尺波涛。顷刻失所。烹鳌于鼎。脔割于俎。于是焉又可笑耶。翁嚬蹙者久之而曰。是则何忍笑。吾为之闷矣。余曰。江河之閒旷。云海之空阔。春风演漾。秋月澄澈。尘杂不侵。渔钓不到。鱼乐其深。跃在浩浩。簸弄山影。呼吸天光。恬波万顷。其游方洋。翁于是以为何如。翁欣然而笑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余笑而作曰。翁之于鱼。有笑有嚬。嚬少于笑。笑于世外。无人与同。则谓之独笑。而名之于堂宜矣。余亦宜从而记之。然何必特撰。请书此堂往复之言以为记。
笱。争入于网。咫尺波涛。顷刻失所。烹鳌于鼎。脔割于俎。于是焉又可笑耶。翁嚬蹙者久之而曰。是则何忍笑。吾为之闷矣。余曰。江河之閒旷。云海之空阔。春风演漾。秋月澄澈。尘杂不侵。渔钓不到。鱼乐其深。跃在浩浩。簸弄山影。呼吸天光。恬波万顷。其游方洋。翁于是以为何如。翁欣然而笑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余笑而作曰。翁之于鱼。有笑有嚬。嚬少于笑。笑于世外。无人与同。则谓之独笑。而名之于堂宜矣。余亦宜从而记之。然何必特撰。请书此堂往复之言以为记。晚悟堂记
光山子隐于甲川。而修身教子孙。力田自食。近名其堂曰晚悟。要余记。余诘之曰。子少游京师。而长居山谷。其于朝野。必已熟其物情矣。岂尝健羡乎富贵之荣焰。声色之芬华。而卒之瞷其滥科巧宦之招灾。盛权大势之起祸。而厚嗜浓欢之罹殃。隆赫之为冷落。快乐之为悲苦。而始悟其不可为耶。亦尝钦慕乎道学之标望。文章之光宠。而终之闻其利根善萌之有杂。狂慧浮艳之匪实。而群疑众恶之四集。问誉之为讥骂。荐延之为挤陷。而始悟其不可好耶。光山子笑曰。彼之如彼。早已料之。则何待晚而始悟哉。顾吾夙
霅桥集卷四 第 518H 页
 龄。颇有区区之志。读书求道。以圣人为必可企。而匡君善世。以天下为不可忘。自中岁困于疢疾。而学无由成。亦见天下之事。有末如之何者。而自断此生以老于百亩之中矣。今也白首穷林。思有得焉。圣人虽不可及。而不可以病自堕。而不慕乎圣人。天下虽不可匡。而不可以穷自外。而不志于天下。吾惟有闭门讲道。随分自治。而训子迪孙。继为善士。欲其知凡人希圣贤之道。寸心受天下之责而已耳。所谓晚而悟者此也。余不觉洒然而叹曰。有是哉子之贤也。士之事固在于遵尧舜之道。而尧舜吾君。尧舜吾民。亦无非士之职也。然而体道在身。行道在时。时之塞也。而子知自废则智也。身而存也。而子知自强则仁也。呜呼。天下不能常治之。亦不当常乱。其治也由行道之有族。其乱也须体道之有种。种之真传族则乃蕃。以子之仁智。穷而独善。以传之子孙者。将自一而为百族。自百而为万族。安知其终不遇时。而不为兼善天下之种耶。子其勉之。大自大也。小自小也。无实之文章。子必视之以夜郎。驴非驴也。马非马也。挟私之道学。子必视之以龟玆。不义之贵。子必比之于鸺鹠之昏飞。不仁之富。子必比之于蜣螂之秽饱。曩吾之诘
龄。颇有区区之志。读书求道。以圣人为必可企。而匡君善世。以天下为不可忘。自中岁困于疢疾。而学无由成。亦见天下之事。有末如之何者。而自断此生以老于百亩之中矣。今也白首穷林。思有得焉。圣人虽不可及。而不可以病自堕。而不慕乎圣人。天下虽不可匡。而不可以穷自外。而不志于天下。吾惟有闭门讲道。随分自治。而训子迪孙。继为善士。欲其知凡人希圣贤之道。寸心受天下之责而已耳。所谓晚而悟者此也。余不觉洒然而叹曰。有是哉子之贤也。士之事固在于遵尧舜之道。而尧舜吾君。尧舜吾民。亦无非士之职也。然而体道在身。行道在时。时之塞也。而子知自废则智也。身而存也。而子知自强则仁也。呜呼。天下不能常治之。亦不当常乱。其治也由行道之有族。其乱也须体道之有种。种之真传族则乃蕃。以子之仁智。穷而独善。以传之子孙者。将自一而为百族。自百而为万族。安知其终不遇时。而不为兼善天下之种耶。子其勉之。大自大也。小自小也。无实之文章。子必视之以夜郎。驴非驴也。马非马也。挟私之道学。子必视之以龟玆。不义之贵。子必比之于鸺鹠之昏飞。不仁之富。子必比之于蜣螂之秽饱。曩吾之诘霅桥集卷四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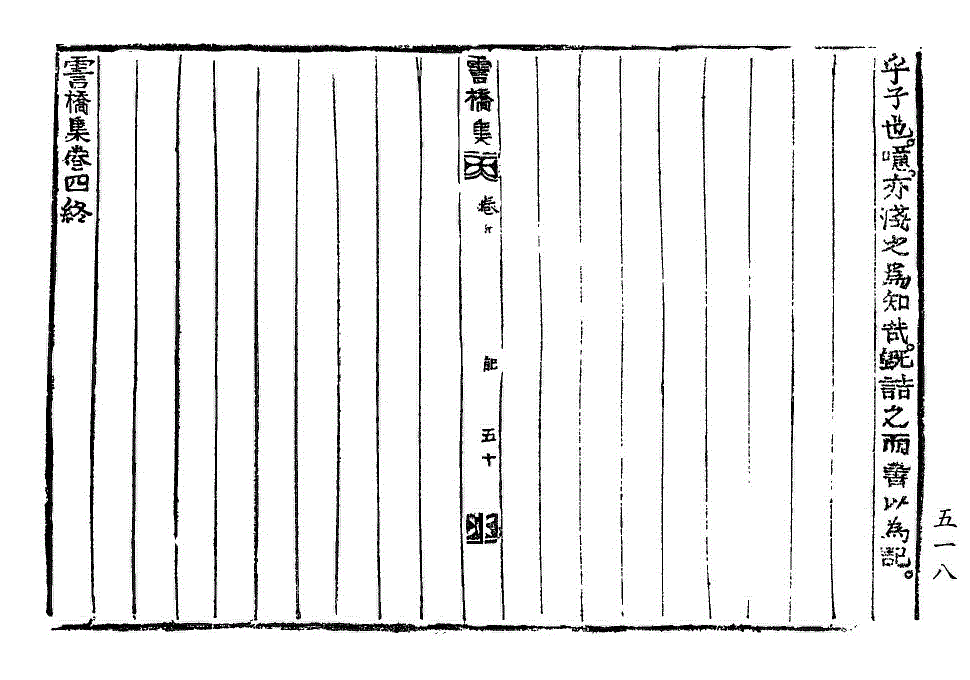 乎子也。噫。亦浅之为知哉。既诘之而书以为记。
乎子也。噫。亦浅之为知哉。既诘之而书以为记。霅桥集卷四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