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x 页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书
书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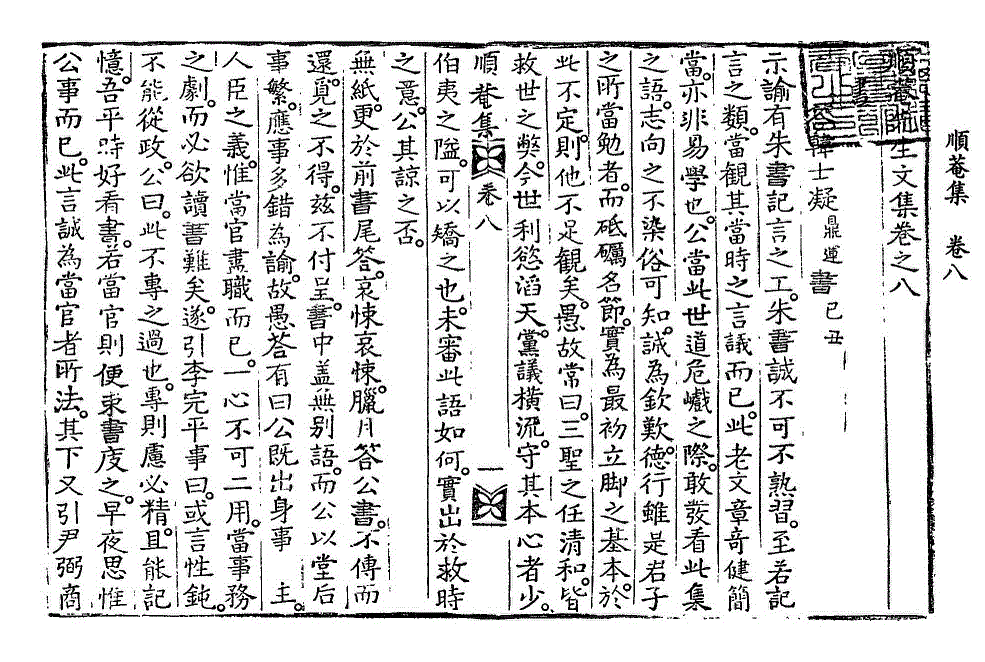 答韩士凝(鼎运)书(己丑)
答韩士凝(鼎运)书(己丑)示谕有朱书记言之工。朱书诚不可不熟习。至若记言之类。当观其当时之言议而已。此老文章奇健简当。亦非易学也。公当此世道危巇之际。敢发看此集之语。志向之不染俗可知。诚为钦叹。德行虽是君子之所当勉者。而砥砺名节。实为最初立脚之基本。于此不定。则他不足观矣。愚故常曰。三圣之任清和。皆救世之弊。今世利欲滔天。党议横流。守其本心者少。伯夷之隘。可以矫之也。未审此语如何。实出于救时之意。公其谅之否。
无纸。更于前书尾答。哀悚哀悚。腊月答公书。不传而还。觅之不得。玆不付呈。书中盖无别语。而公以堂后事繁。应事多错为谕。故愚答有曰公既出身事 主。人臣之义。惟当官尽职而已。一心不可二用。当事务之剧。而必欲读书难矣。遂引李完平事曰。或言性钝。不能从政。公曰。此不专之过也。专则虑必精。且能记忆。吾平时好看书。若当官则便束书庋之。早夜思惟公事而已。此言诚为当官者所法。其下又引尹弼商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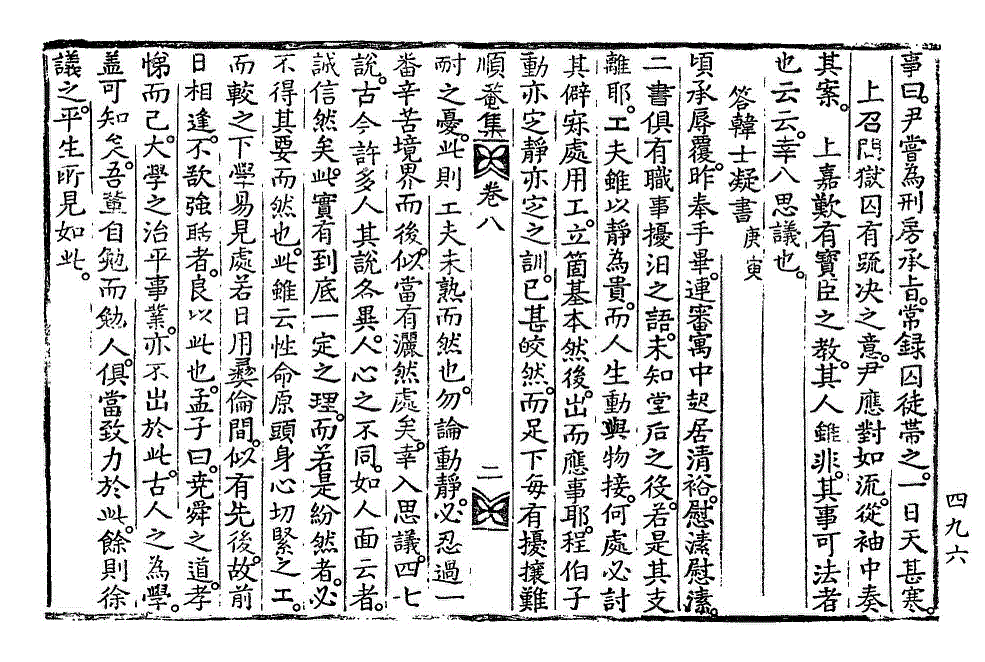 事曰。尹尝为刑房承旨。常录囚徒带之。一日天甚寒。 上召问狱囚有疏决之意。尹应对如流。从袖中奏其案。 上嘉叹有宝臣之教。其人虽非。其事可法者也云云。幸入思议也。
事曰。尹尝为刑房承旨。常录囚徒带之。一日天甚寒。 上召问狱囚有疏决之意。尹应对如流。从袖中奏其案。 上嘉叹有宝臣之教。其人虽非。其事可法者也云云。幸入思议也。答韩士凝书(庚寅)
顷承辱覆。昨奉手毕。连审寓中起居清裕。慰溸慰溸。二书俱有职事扰汨之语。未知堂后之役。若是其支离耶。工夫虽以静为贵。而人生动与物接。何处必讨其僻寂处用工。立个基本然后。出而应事耶。程伯子动亦定静亦定之训。已甚皎然。而足下每有扰攘难耐之忧。此则工夫未熟而然也。勿论动静。必忍过一番辛苦境界而后。似当有洒然处矣。幸入思议。四七说。古今许多人其说各异。人心之不同。如人面云者。诚信然矣。此实有到底一定之理。而若是纷然者。必不得其要而然也。此虽云性命原头身心切紧之工。而较之下学易见处若日用彝伦间。似有先后。故前日相逢。不欲强聒者。良以此也。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大学之治平事业。亦不出于此。古人之为学。盖可知矣。吾辈自勉而勉人。俱当致力于此。馀则徐议之。平生所见如此。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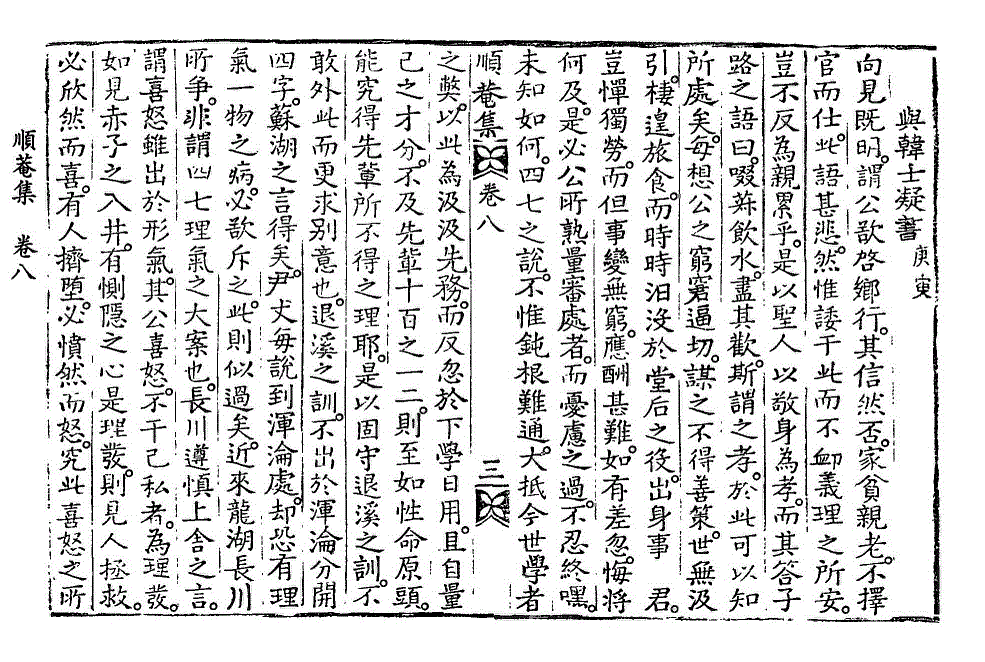 与韩士凝书(庚寅)
与韩士凝书(庚寅)向见既明。谓公欲启乡行。其信然否。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此语甚悲。然惟诿于此而不恤义理之所安。岂不反为亲累乎。是以圣人以敬身为孝。而其答子路之语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于此可以知所处矣。每想公之穷窘逼切。谋之不得善策。世无汲引。栖遑旅食。而时时汨没于堂后之役。出身事 君。岂惮独劳。而但事变无穷。应酬甚难。如有差忽。悔将何及。是必公所熟量审处者。而忧虑之过。不忍终嘿。未知如何。四七之说。不惟钝根难通。大抵今世学者之弊。以此为汲汲先务。而反忽于下学日用。且自量己之才分。不及先辈十百之一二。则至如性命原头。能究得先辈所不得之理耶。是以固守退溪之训。不敢外此而更求别意也。退溪之训。不出于浑沦分开四字。苏湖之言得矣。尹丈每说到浑沦处。却恐有理气一物之病。必欲斥之。此则似过矣。近来龙湖长川所争。非谓四七理气之大案也。长川遵慎上舍之言。谓喜怒虽出于形气。其公喜怒。不干己私者。为理发。如见赤子之入井。有恻隐之心是理发。则见人拯救。必欣然而喜。有人挤堕。必愤然而怒。究此喜怒之所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7L 页
 从来。则与恻隐何别。其为理发无疑。此与高峰后论中节之情归之理发。又不同矣。尹丈矢口力排其说。皆有根据。愚昧于此无定见。故不敢有可否。欲待浅见之或进而究之耳。俯询四七。但泛问而无条列者。未知盛意之何在。而略具彼此是非处。别纸以告。非敢谓有得。欲为讲讨相发之资耳。
从来。则与恻隐何别。其为理发无疑。此与高峰后论中节之情归之理发。又不同矣。尹丈矢口力排其说。皆有根据。愚昧于此无定见。故不敢有可否。欲待浅见之或进而究之耳。俯询四七。但泛问而无条列者。未知盛意之何在。而略具彼此是非处。别纸以告。非敢谓有得。欲为讲讨相发之资耳。别纸
性是人物禀受之名。是形气以后所生。中庸章句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也。(语类又曰。古人制字。先制得一个心字。性与情皆从心。)性既堕在形气中。则气质之性为用。而气质性中。推出本然之性。即理之所在也。于是与气质相分为二名。(气质本出于本然之性。是一性而涉于形气然后。谓之气质之性。)是犹心一也。分而言之。有人道之别。情一也。分而言之。有四七之异。属于理边者。谓之理发。属于形气者。谓之气发。浑沦分开如是而已。前后诸说之纷纷。只成一场说话。似未有十分明快者。故敢陈瞽见。
答韩士凝书(乙未)
朱子尝与辅汉卿书。云汉卿身在都城声利场中。能闭门自守。味众人之所不味。今玩盛书。慥慥为学之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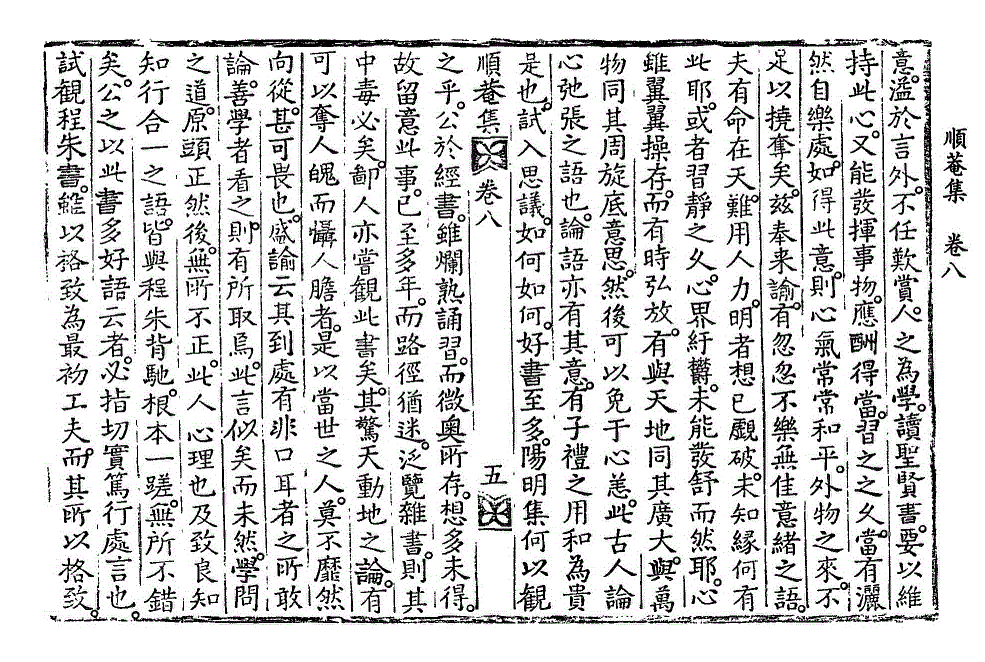 意。溢于言外。不任叹赏。人之为学。读圣贤书。要以维持此心。又能发挥事物。应酬得当。习之之久。当有洒然自乐处。如得此意。则心气常常和平。外物之来。不足以挠夺矣。玆奉来谕。有忽忽不乐无佳意绪之语。夫有命在天。难用人力。明者想已觑破。未知缘何有此耶。或者习静之久。心界纡郁。未能发舒而然耶。心虽翼翼操存。而有时弘放。有与天地同其广大。与万物同其周旋底意思。然后可以免于心恙。此古人论心弛张之语也。论语亦有其意。有子礼之用和为贵是也。试入思议。如何如何。好书至多。阳明集何以观之乎。公于经书。虽烂熟诵习。而微奥所存。想多未得。故留意此事。已至多年。而路径犹迷。泛览杂书。则其中毒必矣。鄙人亦尝观此书矣。其惊天动地之论。有可以夺人魄而慑人胆者。是以当世之人。莫不靡然向从。甚可畏也。盛谕云其到处有非口耳者之所敢论。善学者看之。则有所取焉。此言似矣而未然。学问之道。原头正然后。无所不正。此人心理也及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语。皆与程朱背驰。根本一蹉。无所不错矣。公之以此书多好语云者。必指切实笃行处言也。试观程朱书。虽以格致为最初工夫。而其所以格致。
意。溢于言外。不任叹赏。人之为学。读圣贤书。要以维持此心。又能发挥事物。应酬得当。习之之久。当有洒然自乐处。如得此意。则心气常常和平。外物之来。不足以挠夺矣。玆奉来谕。有忽忽不乐无佳意绪之语。夫有命在天。难用人力。明者想已觑破。未知缘何有此耶。或者习静之久。心界纡郁。未能发舒而然耶。心虽翼翼操存。而有时弘放。有与天地同其广大。与万物同其周旋底意思。然后可以免于心恙。此古人论心弛张之语也。论语亦有其意。有子礼之用和为贵是也。试入思议。如何如何。好书至多。阳明集何以观之乎。公于经书。虽烂熟诵习。而微奥所存。想多未得。故留意此事。已至多年。而路径犹迷。泛览杂书。则其中毒必矣。鄙人亦尝观此书矣。其惊天动地之论。有可以夺人魄而慑人胆者。是以当世之人。莫不靡然向从。甚可畏也。盛谕云其到处有非口耳者之所敢论。善学者看之。则有所取焉。此言似矣而未然。学问之道。原头正然后。无所不正。此人心理也及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语。皆与程朱背驰。根本一蹉。无所不错矣。公之以此书多好语云者。必指切实笃行处言也。试观程朱书。虽以格致为最初工夫。而其所以格致。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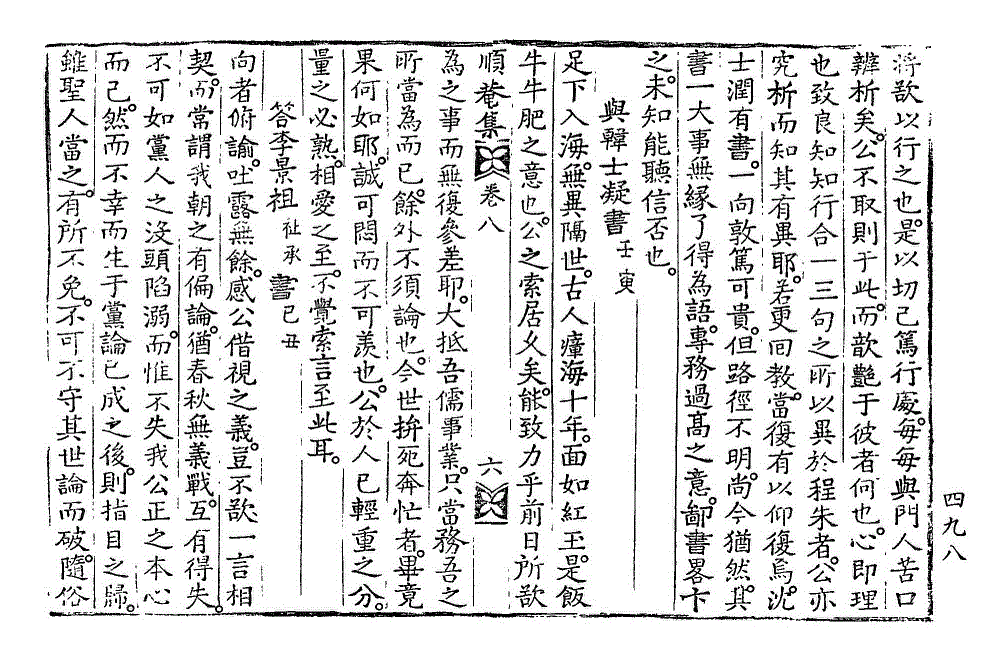 将欲以行之也。是以切己笃行处。每每与门人苦口辨析矣。公不取则于此。而歆艳于彼者何也。心即理也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句之所以异于程朱者。公亦究析而知其有异耶。若更回教。当复有以仰复焉。沈士润有书。一向敦笃可贵。但路径不明。尚今犹然。其书一大事无缘了得为语。专务过高之意。鄙书略卞之。未知能听信否也。
将欲以行之也。是以切己笃行处。每每与门人苦口辨析矣。公不取则于此。而歆艳于彼者何也。心即理也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句之所以异于程朱者。公亦究析而知其有异耶。若更回教。当复有以仰复焉。沈士润有书。一向敦笃可贵。但路径不明。尚今犹然。其书一大事无缘了得为语。专务过高之意。鄙书略卞之。未知能听信否也。与韩士凝书(壬寅)
足下入海。无异隔世。古人瘴海十年。面如红玉。是饭牛牛肥之意也。公之索居久矣。能致力乎前日所欲为之事而无复参差耶。大抵吾儒事业。只当务吾之所当为而已。馀外不须论也。今世拚死奔忙者。毕竟果何如耶。诚可闷而不可羡也。公于人己轻重之分。量之必熟。相爱之至。不觉索言至此耳。
答李景祖(祉承)书(己丑)
向者俯谕。吐露无馀。感公借视之义。岂不欲一言相契。而常谓我朝之有偏论。犹春秋无义战。互有得失。不可如党人之没头陷溺。而惟不失我公正之本心而已。然而不幸而生于党论已成之后。则指目之归。虽圣人当之。有所不免。不可不守其世论而破。随俗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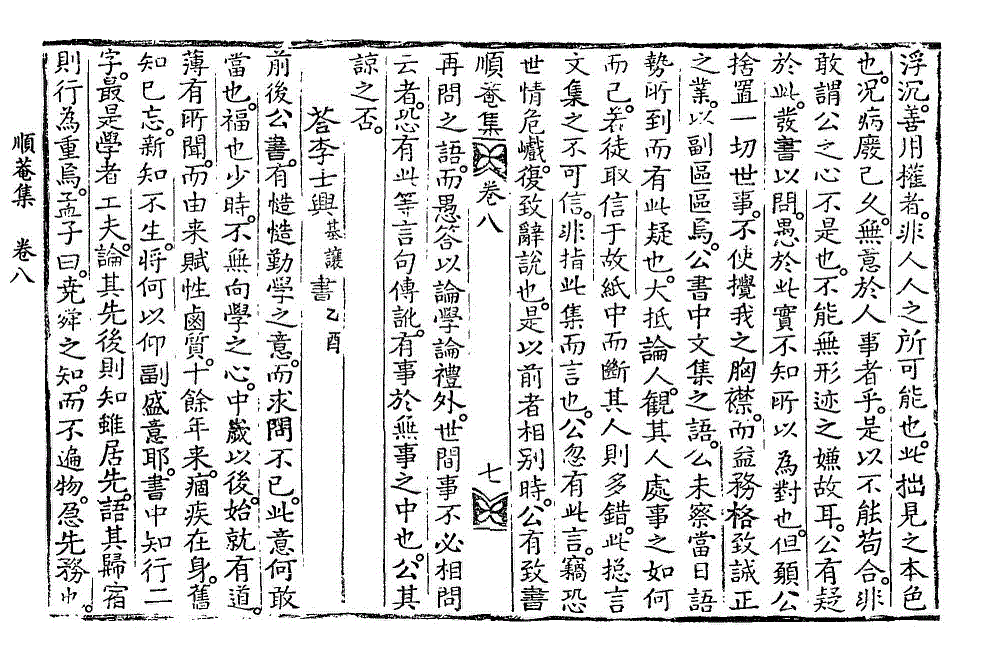 浮沉。善用权者。非人人之所可能也。此拙见之本色也。况病废已久。无意于人事者乎。是以不能苟合。非敢谓公之心不是也。不能无形迹之嫌故耳。公有疑于此。发书以问。愚于此实不知所以为对也。但愿公舍置一切世事。不使搅我之胸襟。而益务格致诚正之业。以副区区焉。公书中文集之语。公未察当日语势所到而有此疑也。大抵论人。观其人处事之如何而已。若徒取信于故纸中而断其人则多错。此总言文集之不可信。非指此集而言也。公忽有此言。窃恐世情危巇。复致辞说也。是以前者相别时。公有致书再问之语。而愚答以论学论礼外。世间事不必相问云者。恐有此等言句传讹。有事于无事之中也。公其谅之否。
浮沉。善用权者。非人人之所可能也。此拙见之本色也。况病废已久。无意于人事者乎。是以不能苟合。非敢谓公之心不是也。不能无形迹之嫌故耳。公有疑于此。发书以问。愚于此实不知所以为对也。但愿公舍置一切世事。不使搅我之胸襟。而益务格致诚正之业。以副区区焉。公书中文集之语。公未察当日语势所到而有此疑也。大抵论人。观其人处事之如何而已。若徒取信于故纸中而断其人则多错。此总言文集之不可信。非指此集而言也。公忽有此言。窃恐世情危巇。复致辞说也。是以前者相别时。公有致书再问之语。而愚答以论学论礼外。世间事不必相问云者。恐有此等言句传讹。有事于无事之中也。公其谅之否。答李士兴(基让)书(乙酉)
前后公书。有慥慥勤学之意。而求问不已。此意何敢当也。福也少时。不无向学之心。中岁以后。始就有道。薄有所闻。而由来赋性卤质。十馀年来。痼疾在身。旧知已忘。新知不生。将何以仰副盛意耶。书中知行二字。最是学者工夫。论其先后则知虽居先。语其归宿则行为重焉。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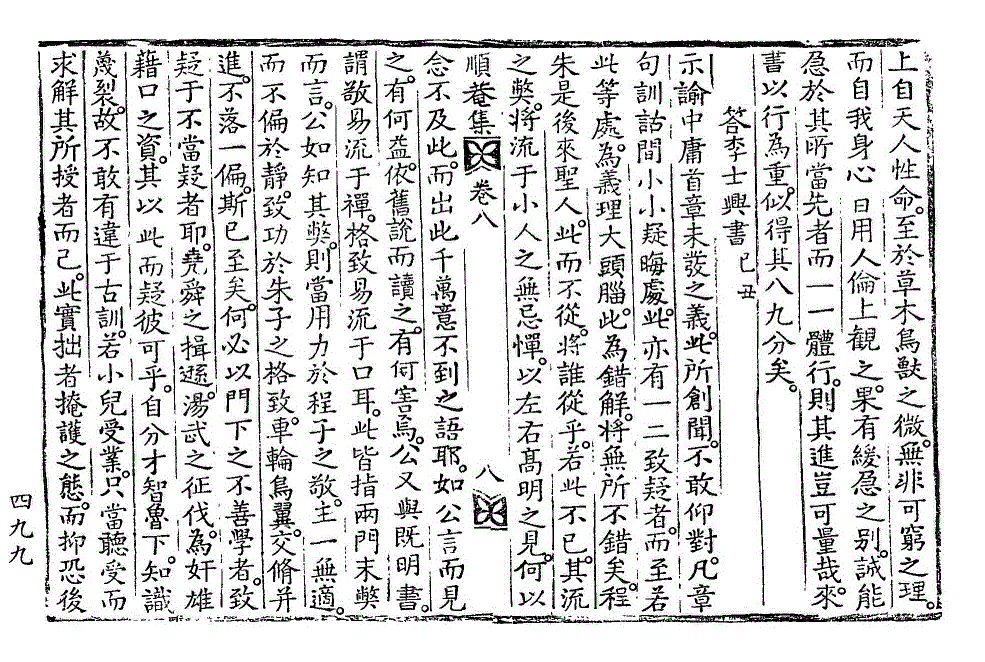 上自天人性命。至于草木鸟兽之微。无非可穷之理。而自我身心日用人伦上观之。果有缓急之别。诚能急于其所当先者而一一体行。则其进岂可量哉。来书以行为重。似得其八九分矣。
上自天人性命。至于草木鸟兽之微。无非可穷之理。而自我身心日用人伦上观之。果有缓急之别。诚能急于其所当先者而一一体行。则其进岂可量哉。来书以行为重。似得其八九分矣。答李士兴书(己丑)
示谕中庸首章未发之义。此所创闻。不敢仰对。凡章句训诂间小小疑晦处。此亦有一二致疑者。而至若此等处。为义理大头脑。此为错解。将无所不错矣。程朱是后来圣人。此而不从。将谁从乎。若此不已。其流之弊。将流于小人之无忌惮。以左右高明之见。何以念不及此。而出此千万意不到之语耶。如公言而见之。有何益。依旧说而读之。有何害焉。公又与既明书。谓敬易流于禅。格致易流于口耳。此皆指两门末弊而言。公如知其弊。则当用力于程子之敬。主一无适。而不偏于静。致功于朱子之格致。车轮鸟翼。交脩并进。不落一偏。斯已至矣。何必以门下之不善学者。致疑于不当疑者耶。尧舜之揖逊。汤武之征伐。为奸雄藉口之资。其以此而疑彼可乎。自分才智鲁下。知识蔑裂。故不敢有违于古训。若小儿受业。只当听受而求解其所授者而已。此实拙者掩护之态。而抑恐后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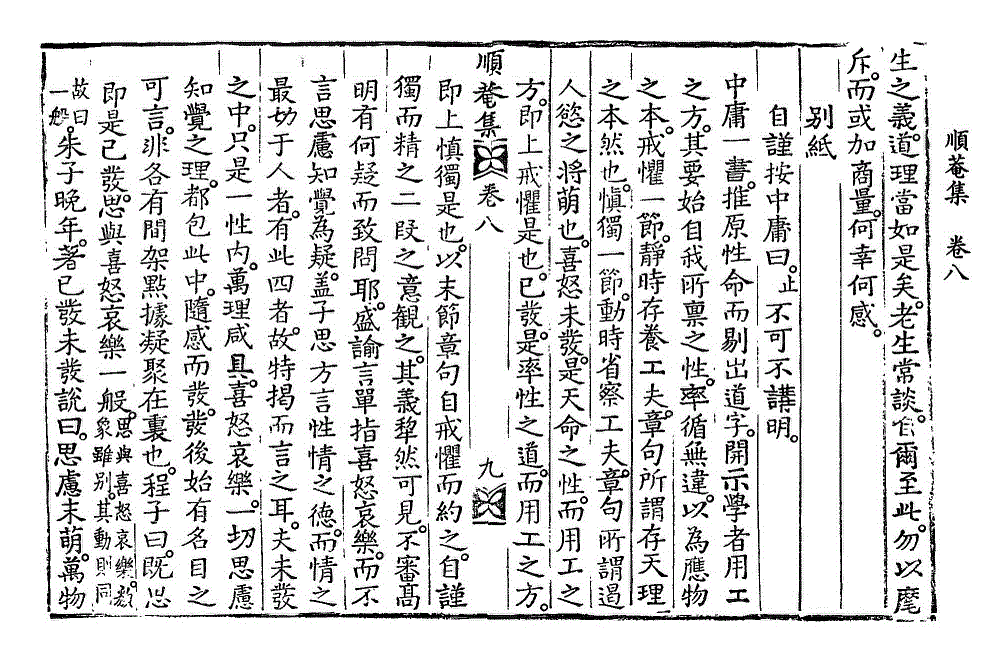 生之义。道理当如是矣。老生常谈。自尔至此。勿以麾斥。而或加商量。何幸何感。
生之义。道理当如是矣。老生常谈。自尔至此。勿以麾斥。而或加商量。何幸何感。别纸
自谨按中庸曰。(止)不可不讲明。
中庸一书。推原性命而剔出道字。开示学者用工之方。其要始自我所禀之性。率循无违。以为应物之本。戒惧一节。静时存养工夫。章句所谓存天理之本然也。慎独一节。动时省察工夫。章句所谓遏人欲之将萌也。喜怒未发。是天命之性。而用工之方。即上戒惧是也。已发。是率性之道。而用工之方。即上慎独是也。以末节章句自戒惧而约之。自谨独而精之二段之意观之。其义犁然可见。不审高明有何疑而致问耶。盛谕言单指喜怒哀乐。而不言思虑知觉为疑。盖子思方言性情之德。而情之最切于人者。有此四者。故特揭而言之耳。夫未发之中。只是一性内。万理咸具。喜怒哀乐。一切思虑知觉之理。都包此中。随感而发。发后始有名目之可言。非各有间架点据凝聚在里也。程子曰。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思与喜怒哀乐。貌象虽别。其动则同故曰一般。)朱子晚年。著已发未发说曰。思虑未萌。万物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0L 页
 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观此二说。则其发未发之意较然矣。中字义。详于朱子答张南轩中和第六书。试取而观之。窃观来意。以中为不作未发看。盛谕有云动作言语。一皆中正。而特一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而言。未审此有古语耶。抑公自得之见耶。虽是古语。已悖于子思之意。而动作言语。一皆中正。是为发而中节之时。岂可言于未发之中耶。若是自得。则恐是千虑之一失。凡看书之法。先观文势。次观文义。必寻讨平正明白处去。何必艰曲深险。求昔贤不言之意而自以为得乎。且使吾之自得者。求之义理。求之用工之方。实有质神明而无疑者。则信之宜矣。今以章句所释观之。其动静相涵。表里交养。无所亏阙。可谓绝渗漏无病败。其比于公之所疑。孰优孰劣。孰得孰失。孰为切实。孰为歇后。通下诸说而观之。公于未发之中。必欲异于前人。而以中为已发。如是看。其有何十分道理。而其于用工之实事。能有过于本注之义乎。
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观此二说。则其发未发之意较然矣。中字义。详于朱子答张南轩中和第六书。试取而观之。窃观来意。以中为不作未发看。盛谕有云动作言语。一皆中正。而特一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而言。未审此有古语耶。抑公自得之见耶。虽是古语。已悖于子思之意。而动作言语。一皆中正。是为发而中节之时。岂可言于未发之中耶。若是自得。则恐是千虑之一失。凡看书之法。先观文势。次观文义。必寻讨平正明白处去。何必艰曲深险。求昔贤不言之意而自以为得乎。且使吾之自得者。求之义理。求之用工之方。实有质神明而无疑者。则信之宜矣。今以章句所释观之。其动静相涵。表里交养。无所亏阙。可谓绝渗漏无病败。其比于公之所疑。孰优孰劣。孰得孰失。孰为切实。孰为歇后。通下诸说而观之。公于未发之中。必欲异于前人。而以中为已发。如是看。其有何十分道理。而其于用工之实事。能有过于本注之义乎。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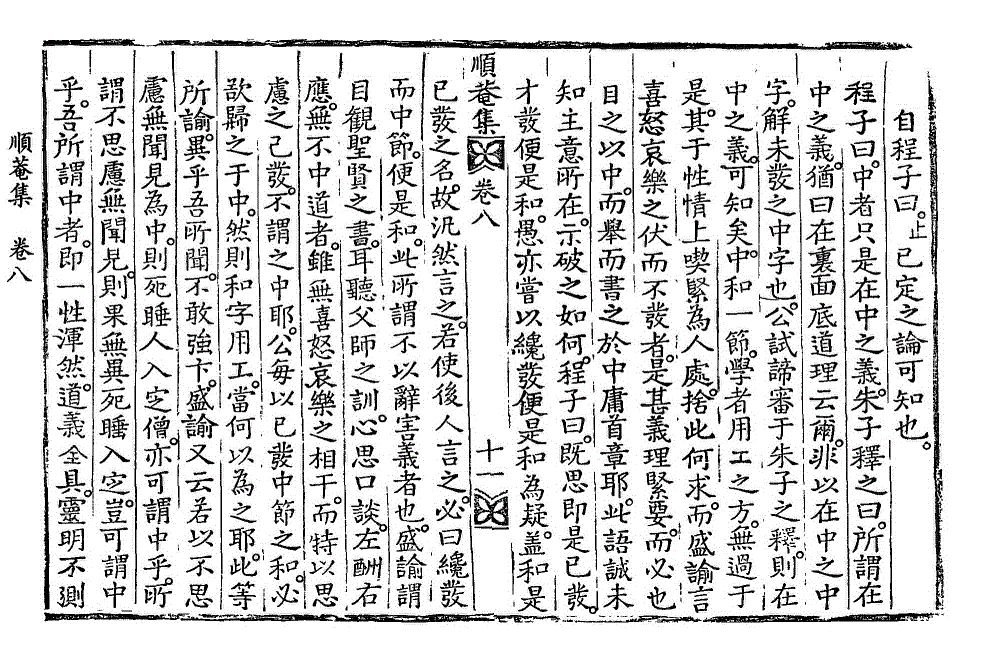 自程子曰。(止)已定之论可知也。
自程子曰。(止)已定之论可知也。程子曰。中者只是在中之义。朱子释之曰。所谓在中之义。犹曰在里面底道理云尔。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发之中字也。公试谛审于朱子之释。则在中之义。可知矣。中和一节。学者用工之方。无过于是。其于性情上吃紧为人处。舍此何求。而盛谕言喜怒哀乐之伏而不发者。是甚义理紧要。而必也目之以中。而举而书之于中庸首章耶。此语诚未知主意所在。示破之如何。程子曰。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是和。愚亦尝以才发便是和为疑。盖和是已发之名。故汎然言之。若使后人言之。必曰才发而中节。便是和。此所谓不以辞害义者也。盛谕谓目观圣贤之书。耳听父师之训。心思口谈。左酬右应。无不中道者。虽无喜怒哀乐之相干。而特以思虑之已发。不谓之中耶。公每以已发中节之和。必欲归之于中。然则和字用工。当何以为之耶。此等所谕。异乎吾所闻。不敢强卞。盛谕又云若以不思虑无闻见为中。则死睡人入定僧。亦可谓中乎。所谓不思虑无闻见。则果无异死睡入定。岂可谓中乎。吾所谓中者。即一性浑然。道义全具。灵明不测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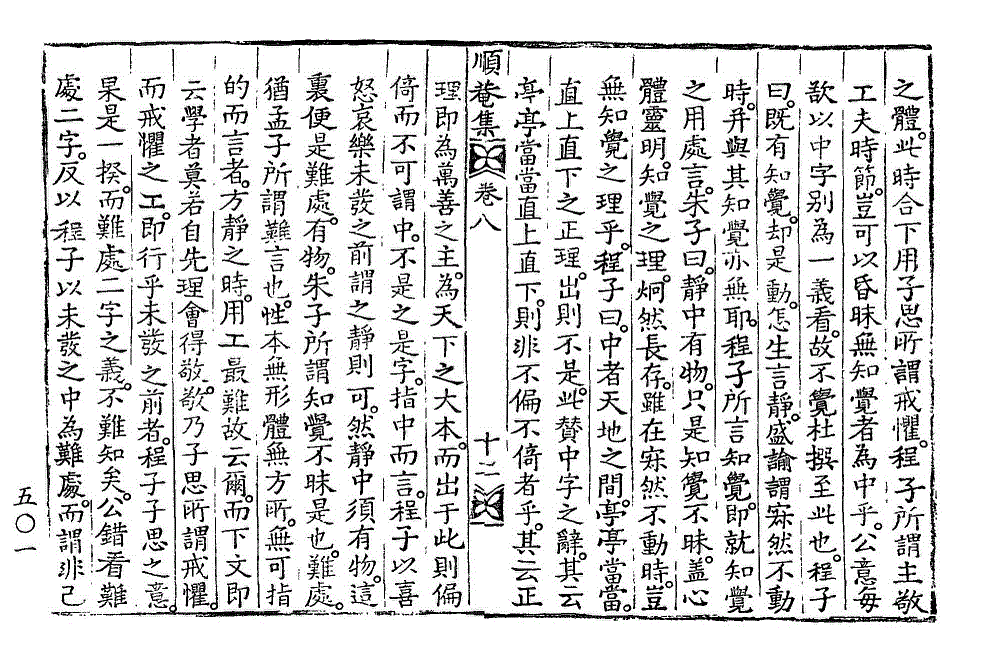 之体。此时合下用子思所谓戒惧。程子所谓主敬工夫时节。岂可以昏昧无知觉者为中乎。公意每欲以中字别为一义看。故不觉杜撰至此也。程子曰。既有知觉。却是动。怎生言静。盛谕谓寂然不动时。并与其知觉亦无耶。程子所言知觉。即就知觉之用处言。朱子曰。静中有物。只是知觉不昧。盖心体灵明。知觉之理。炯然长存。虽在寂然不动时。岂无知觉之理乎。程子曰。中者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此赞中字之辞。其云亭亭当当直上直下。则非不偏不倚者乎。其云正理即为万善之主。为天下之大本。而出于此则偏倚而不可谓中。不是之是字。指中而言。程子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这里便是难处。有物。朱子所谓知觉不昧是也。难处。犹孟子所谓难言也。性本无形体无方所。无可指的而言者。方静之时。用工最难故云尔。而下文即云学者莫若自先理会得敬。敬乃子思所谓戒惧。而戒惧之工。即行乎未发之前者。程子子思之意。果是一揆。而难处二字之义。不难知矣。公错看难处二字。反以程子以未发之中为难处。而谓非已
之体。此时合下用子思所谓戒惧。程子所谓主敬工夫时节。岂可以昏昧无知觉者为中乎。公意每欲以中字别为一义看。故不觉杜撰至此也。程子曰。既有知觉。却是动。怎生言静。盛谕谓寂然不动时。并与其知觉亦无耶。程子所言知觉。即就知觉之用处言。朱子曰。静中有物。只是知觉不昧。盖心体灵明。知觉之理。炯然长存。虽在寂然不动时。岂无知觉之理乎。程子曰。中者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此赞中字之辞。其云亭亭当当直上直下。则非不偏不倚者乎。其云正理即为万善之主。为天下之大本。而出于此则偏倚而不可谓中。不是之是字。指中而言。程子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这里便是难处。有物。朱子所谓知觉不昧是也。难处。犹孟子所谓难言也。性本无形体无方所。无可指的而言者。方静之时。用工最难故云尔。而下文即云学者莫若自先理会得敬。敬乃子思所谓戒惧。而戒惧之工。即行乎未发之前者。程子子思之意。果是一揆。而难处二字之义。不难知矣。公错看难处二字。反以程子以未发之中为难处。而谓非已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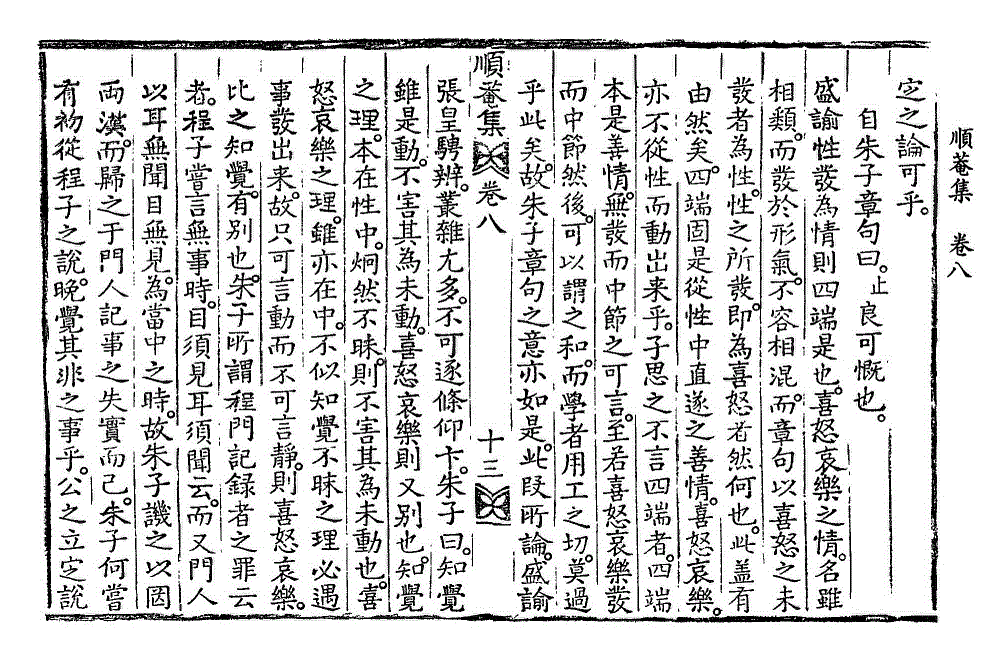 定之论可乎。
定之论可乎。自朱子章句曰。(止)良可慨也。
盛谕性发为情则四端是也。喜怒哀乐之情。名虽相类。而发于形气。不容相混。而章句以喜怒之未发者为性。性之所发。即为喜怒者然何也。此盖有由然矣。四端固是从性中直遂之善情。喜怒哀乐。亦不从性而动出来乎。子思之不言四端者。四端本是善情。无发而中节之可言。至若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然后。可以谓之和。而学者用工之切。莫过乎此矣。故朱子章句之意亦如是。此段所论。盛谕张皇骋辨。丛杂尤多。不可逐条仰卞。朱子曰。知觉虽是动。不害其为未动。喜怒哀乐则又别也。知觉之理。本在性中。炯然不昧。则不害其为未动也。喜怒哀乐之理。虽亦在中。不似知觉不昧之理必遇事发出来。故只可言动而不可言静。则喜怒哀乐。比之知觉。有别也。朱子所谓程门记录者之罪云者。程子尝言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云。而又门人以耳无闻目无见。为当中之时。故朱子讥之以罔两汉。而归之于门人记事之失实而已。朱子何尝有初从程子之说。晚觉其非之事乎。公之立定说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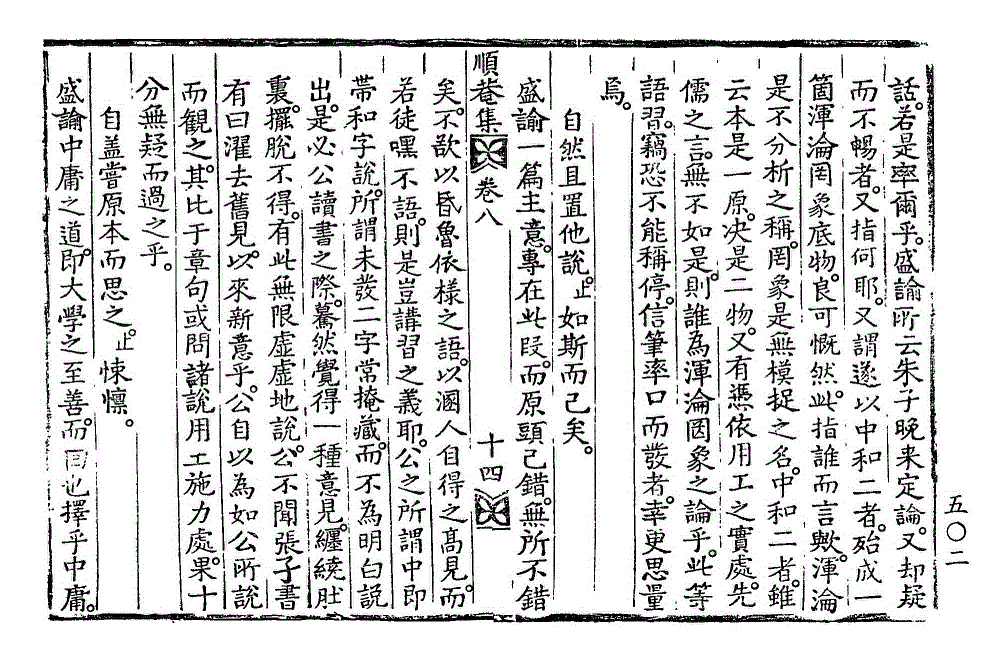 话。若是率尔乎。盛谕所云朱子晚来定论。又却疑而不畅者。又指何耶。又谓遂以中和二者。殆成一个浑沦罔象底物。良可慨然。此指谁而言欤。浑沦是不分析之称。罔象是无模捉之名。中和二者。虽云本是一原。决是二物。又有凭依用工之实处。先儒之言。无不如是。则谁为浑沦罔象之论乎。此等语习。窃恐不能称停。信笔率口而发者。幸更思量焉。
话。若是率尔乎。盛谕所云朱子晚来定论。又却疑而不畅者。又指何耶。又谓遂以中和二者。殆成一个浑沦罔象底物。良可慨然。此指谁而言欤。浑沦是不分析之称。罔象是无模捉之名。中和二者。虽云本是一原。决是二物。又有凭依用工之实处。先儒之言。无不如是。则谁为浑沦罔象之论乎。此等语习。窃恐不能称停。信笔率口而发者。幸更思量焉。自然且置他说。(止)如斯而已矣。
盛谕一篇主意。专在此段。而原头已错。无所不错矣。不欲以昏鲁依样之语。以溷人自得之高见。而若徒嘿不语。则是岂讲习之义耶。公之所谓中即带和字说。所谓未发二字常掩藏。而不为明白说出。是必公读书之际。蓦然觉得一种意见。缠绕肚里。摆脱不得。有此无限虚虚地说。公不闻张子书有曰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乎。公自以为如公所说而观之。其比于章句或问诸说用工施力处。果十分无疑而过之乎。
自盖尝原本而思之。(止)悚懔。
盛谕中庸之道。即大学之至善。而回也择乎中庸。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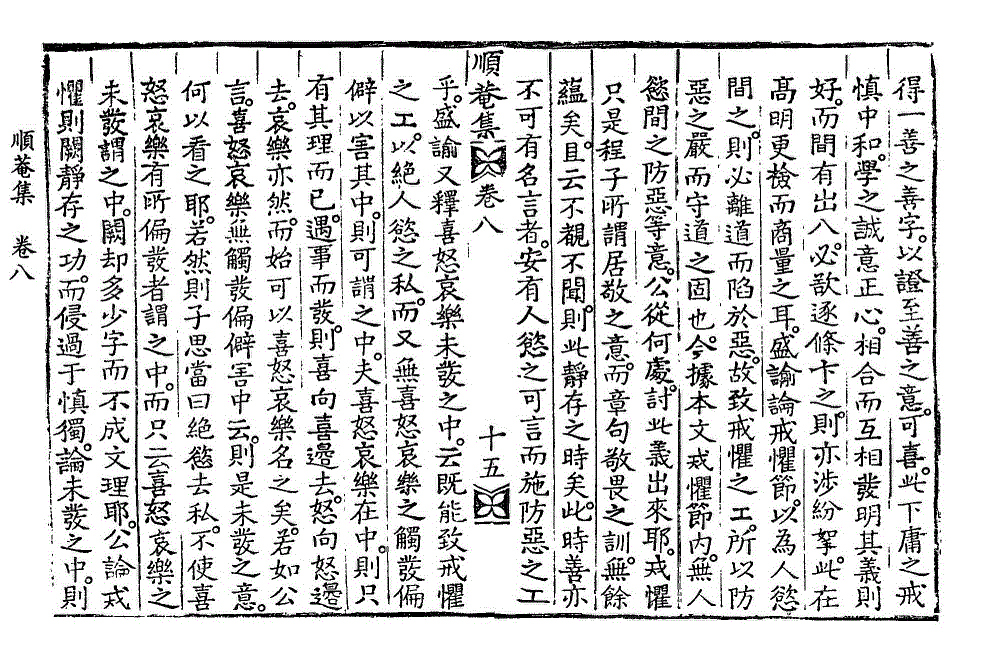 得一善之善字。以證至善之意。可喜。此下庸之戒慎中和。学之诚意正心。相合而互相发明其义则好。而间有出入。必欲逐条卞之。则亦涉纷挐。此在高明更检而商量之耳。盛谕论戒惧节。以为人欲间之。则必离道而陷于恶。故致戒惧之工。所以防恶之严而守道之固也。今据本文戒惧节内。无人欲间之防恶等意。公从何处。讨此义出来耶。戒惧只是程子所谓居敬之意。而章句敬畏之训。无馀蕴矣。且云不睹不闻。则此静存之时矣。此时善亦不可有名言者。安有人欲之可言而施防恶之工乎。盛谕又释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云既能致戒惧之工。以绝人欲之私。而又无喜怒哀乐之触发偏僻以害其中。则可谓之中。夫喜怒哀乐在中。则只有其理而已。遇事而发。则喜向喜边去。怒向怒边去。哀乐亦然。而始可以喜怒哀乐名之矣。若如公言。喜怒哀乐无触发偏僻害中云。则是未发之意。何以看之耶。若然则子思当曰绝欲去私。不使喜怒哀乐有所偏发者谓之中。而只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阙却多少字而不成文理耶。公论戒惧则阙静存之功。而侵过于慎独。论未发之中。则
得一善之善字。以證至善之意。可喜。此下庸之戒慎中和。学之诚意正心。相合而互相发明其义则好。而间有出入。必欲逐条卞之。则亦涉纷挐。此在高明更检而商量之耳。盛谕论戒惧节。以为人欲间之。则必离道而陷于恶。故致戒惧之工。所以防恶之严而守道之固也。今据本文戒惧节内。无人欲间之防恶等意。公从何处。讨此义出来耶。戒惧只是程子所谓居敬之意。而章句敬畏之训。无馀蕴矣。且云不睹不闻。则此静存之时矣。此时善亦不可有名言者。安有人欲之可言而施防恶之工乎。盛谕又释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云既能致戒惧之工。以绝人欲之私。而又无喜怒哀乐之触发偏僻以害其中。则可谓之中。夫喜怒哀乐在中。则只有其理而已。遇事而发。则喜向喜边去。怒向怒边去。哀乐亦然。而始可以喜怒哀乐名之矣。若如公言。喜怒哀乐无触发偏僻害中云。则是未发之意。何以看之耶。若然则子思当曰绝欲去私。不使喜怒哀乐有所偏发者谓之中。而只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阙却多少字而不成文理耶。公论戒惧则阙静存之功。而侵过于慎独。论未发之中。则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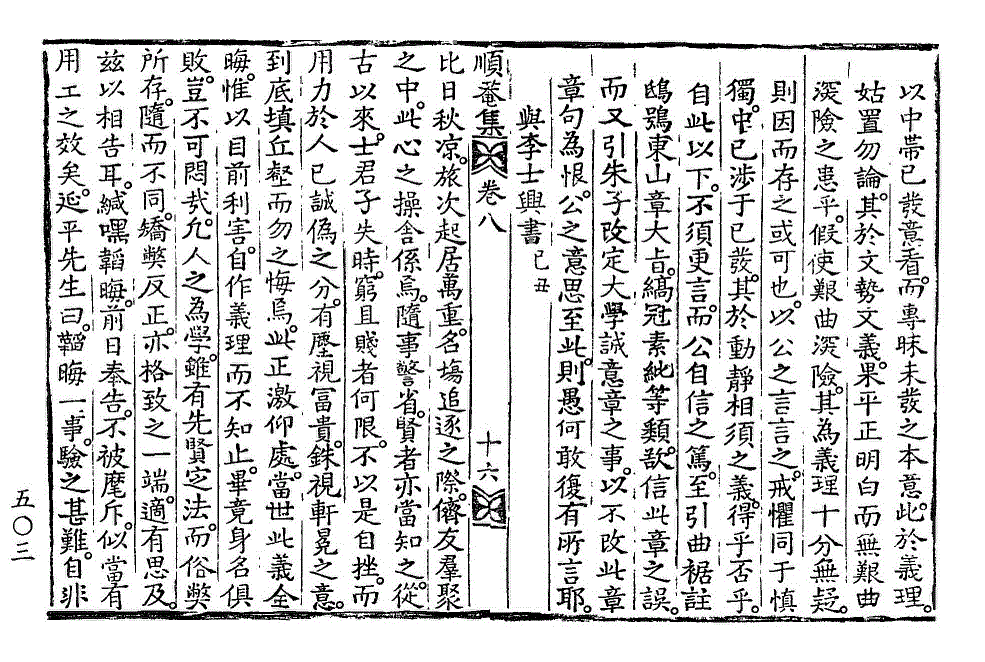 以中带已发意看。而专昧未发之本意。此于义理。姑置勿论。其于文势文义。果平正明白而无艰曲深险之患乎。假使艰曲深险。其为义理十分无疑。则因而存之或可也。以公之言言之。戒惧同于慎独。中已涉于已发。其于动静相须之义。得乎否乎。自此以下。不须更言。而公自信之笃。至引曲裾注鸱鸮东山章大旨。缟冠素纰等类。欲信此章之误。而又引朱子改定大学诚意章之事。以不改此章章句为恨。公之意思至此。则愚何敢复有所言耶。
以中带已发意看。而专昧未发之本意。此于义理。姑置勿论。其于文势文义。果平正明白而无艰曲深险之患乎。假使艰曲深险。其为义理十分无疑。则因而存之或可也。以公之言言之。戒惧同于慎独。中已涉于已发。其于动静相须之义。得乎否乎。自此以下。不须更言。而公自信之笃。至引曲裾注鸱鸮东山章大旨。缟冠素纰等类。欲信此章之误。而又引朱子改定大学诚意章之事。以不改此章章句为恨。公之意思至此。则愚何敢复有所言耶。与李士兴书(己丑)
比日秋凉。旅次起居万重。名场追逐之际。侪友群聚之中。此心之操舍系焉。随事警省。贤者亦当知之。从古以来。士君子失时。穷且贱者何限。不以是自挫。而用力于人己诚伪之分。有尘视富贵。铢视轩冕之意。到底填丘壑而勿之悔焉。此正激仰处。当世此义全晦。惟以目前利害。自作义理而不知止。毕竟身名俱败。岂不可闷哉。凡人之为学。虽有先贤定法。而俗弊所存。随而不同。矫弊反正。亦格致之一端。适有思及。玆以相告耳。缄嘿韬晦。前日奉告。不被麾斥。似当有用工之效矣。延平先生曰。韬晦一事。验之甚难。自非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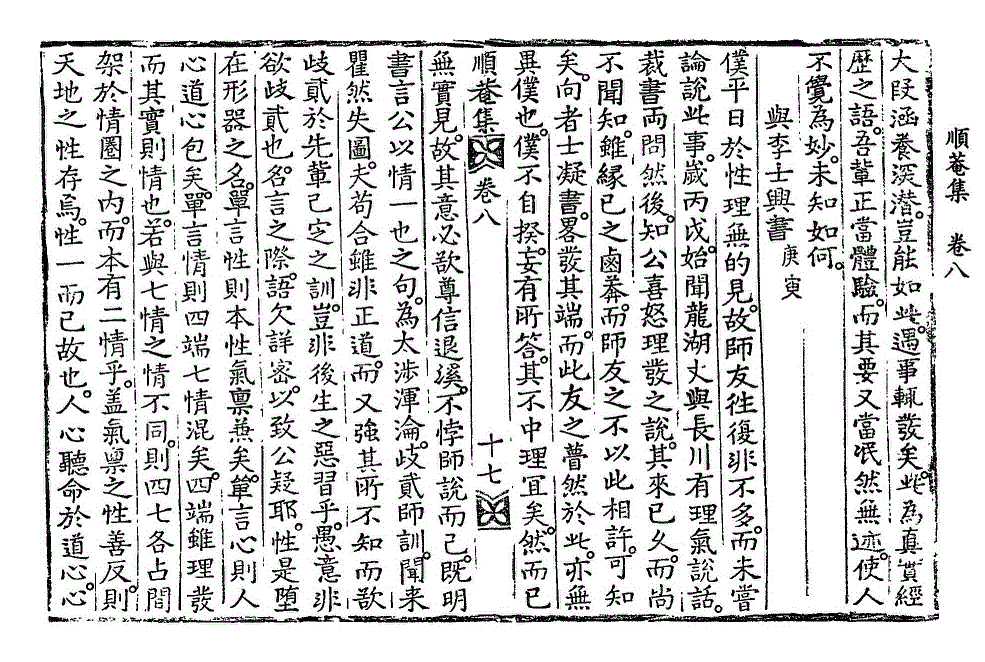 大段涵养深潜。岂能如此。遇事辄发矣。此为真实经历之语。吾辈正当体验。而其要又当泯然无迹。使人不觉为妙。未知如何。
大段涵养深潜。岂能如此。遇事辄发矣。此为真实经历之语。吾辈正当体验。而其要又当泯然无迹。使人不觉为妙。未知如何。与李士兴书(庚寅)
仆平日于性理无的见。故师友往复非不多。而未尝论说此事。岁丙戌。始闻龙湖丈与长川有理气说话。裁书两问然后。知公喜怒理发之说。其来已久。而尚不闻知。虽缘己之卤莽。而师友之不以此相许。可知矣。向者士凝书。略发其端。而此友之瞢然于此。亦无异仆也。仆不自揆。妄有所答。其不中理宜矣。然而己无实见。故其意必欲尊信退溪。不悖师说而已。既明书言公以情一也之句。为太涉浑沦。歧贰师训。闻来瞿然失图。夫苟合虽非正道。而又强其所不知而欲歧贰于先辈已定之训。岂非后生之恶习乎。愚意非欲歧贰也。名言之际。语欠详密。以致公疑耶。性是堕在形器之名。单言性则本性气禀兼矣。单言心则人心道心包矣。单言情则四端七情混矣。四端虽理发而其实则情也。若与七情之情不同。则四七各占间架于情圈之内。而本有二情乎。盖气禀之性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性一而已故也。人心听命于道心。心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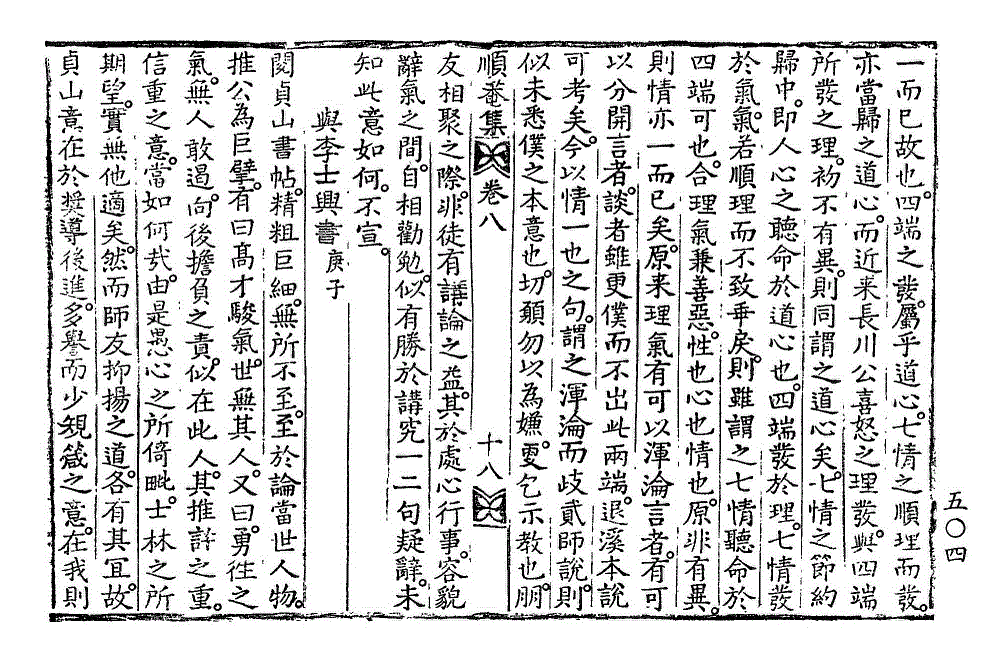 一而已故也。四端之发。属乎道心。七情之顺理而发。亦当归之道心。而近来长川公喜怒之理发。与四端所发之理。初不有异。则同谓之道心矣。七情之节约归中。即人心之听命于道心也。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气若顺理而不致乖戾。则虽谓之七情听命于四端可也。合理气兼善恶。性也心也情也。原非有异。则情亦一而已矣。原来理气有可以浑沦言者。有可以分开言者。谈者虽更仆而不出此两端。退溪本说可考矣。今以情一也之句。谓之浑沦而歧贰师说。则似未悉仆之本意也。切愿勿以为嫌。更乞示教也。朋友相聚之际。非徒有讲论之益。其于处心行事。容貌辞气之间。自相劝勉。似有胜于讲究一二句疑辞。未知此意如何。不宣。
一而已故也。四端之发。属乎道心。七情之顺理而发。亦当归之道心。而近来长川公喜怒之理发。与四端所发之理。初不有异。则同谓之道心矣。七情之节约归中。即人心之听命于道心也。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气若顺理而不致乖戾。则虽谓之七情听命于四端可也。合理气兼善恶。性也心也情也。原非有异。则情亦一而已矣。原来理气有可以浑沦言者。有可以分开言者。谈者虽更仆而不出此两端。退溪本说可考矣。今以情一也之句。谓之浑沦而歧贰师说。则似未悉仆之本意也。切愿勿以为嫌。更乞示教也。朋友相聚之际。非徒有讲论之益。其于处心行事。容貌辞气之间。自相劝勉。似有胜于讲究一二句疑辞。未知此意如何。不宣。与李士兴书(庚子)
阅贞山书帖。精粗巨细。无所不至。至于论当世人物。推公为巨擘。有曰高才骏气。世无其人。又曰。勇往之气。无人敢遏。向后担负之责。似在此人。其推许之重。信重之意。当如何哉。由是愚心之所倚毗。士林之所期望。实无他适矣。然而师友抑扬之道。各有其宜。故贞山意在于奖导后进。多誉而少规箴之意。在我则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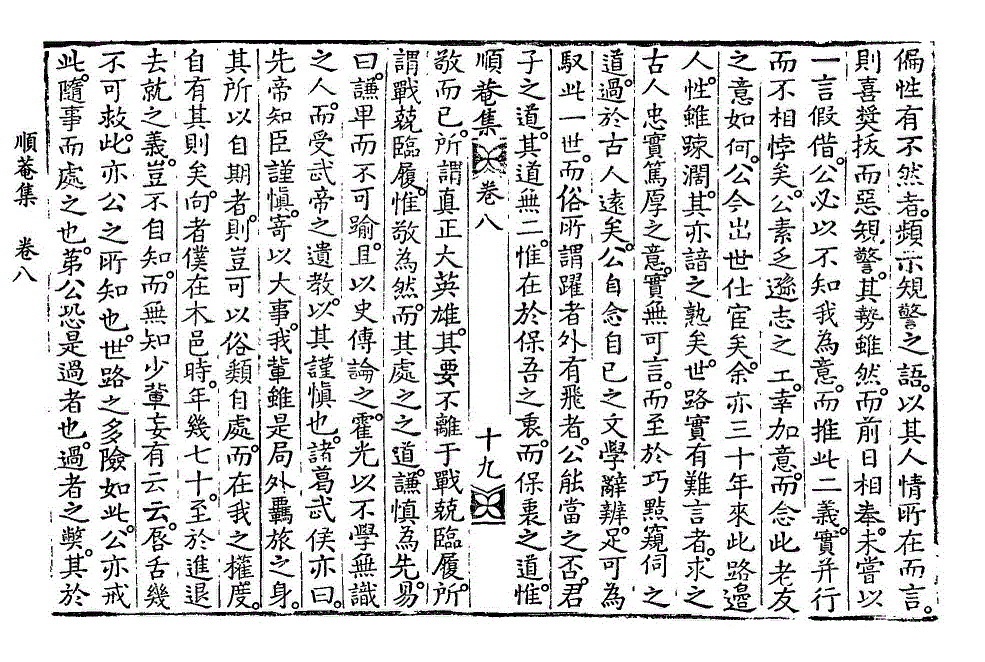 偏性有不然者。频示规警之语。以其人情所在而言。则喜奖拔而恶规警。其势虽然。而前日相奉。未尝以一言假借。公必以不知我为意。而推此二义。实并行而不相悖矣。公素乏逊志之工。幸加意。而念此老友之意如何。公今出世仕宦矣。余亦三十年来此路边人。性虽疏阔。其亦谙之熟矣。世路实有难言者。求之古人忠实笃厚之意。实无可言。而至于巧黠窥伺之道。过于古人远矣。公自念自己之文学辞辨。足可为驭此一世。而俗所谓跃者外有飞者。公能当之否。君子之道。其道无二。惟在于保吾之衷。而保衷之道。惟敬而已。所谓真正大英雄。其要不离于战兢临履。所谓战兢临履。惟敬为然。而其处之之道。谦慎为先。易曰。谦卑而不可踰。且以史传论之。霍光以不学无识之人。而受武帝之遗教。以其谨慎也。诸葛武侯亦曰。先帝知臣谨慎。寄以大事。我辈虽是局外羁旅之身。其所以自期者。则岂可以俗类自处。而在我之权度。自有其则矣。向者仆在木邑时。年几七十。至于进退去就之义。岂不自知。而无知少辈妄有云云。唇舌几不可救。此亦公之所知也。世路之多险如此。公亦戒此。随事而处之也。第公恐是过者也。过者之弊。其于
偏性有不然者。频示规警之语。以其人情所在而言。则喜奖拔而恶规警。其势虽然。而前日相奉。未尝以一言假借。公必以不知我为意。而推此二义。实并行而不相悖矣。公素乏逊志之工。幸加意。而念此老友之意如何。公今出世仕宦矣。余亦三十年来此路边人。性虽疏阔。其亦谙之熟矣。世路实有难言者。求之古人忠实笃厚之意。实无可言。而至于巧黠窥伺之道。过于古人远矣。公自念自己之文学辞辨。足可为驭此一世。而俗所谓跃者外有飞者。公能当之否。君子之道。其道无二。惟在于保吾之衷。而保衷之道。惟敬而已。所谓真正大英雄。其要不离于战兢临履。所谓战兢临履。惟敬为然。而其处之之道。谦慎为先。易曰。谦卑而不可踰。且以史传论之。霍光以不学无识之人。而受武帝之遗教。以其谨慎也。诸葛武侯亦曰。先帝知臣谨慎。寄以大事。我辈虽是局外羁旅之身。其所以自期者。则岂可以俗类自处。而在我之权度。自有其则矣。向者仆在木邑时。年几七十。至于进退去就之义。岂不自知。而无知少辈妄有云云。唇舌几不可救。此亦公之所知也。世路之多险如此。公亦戒此。随事而处之也。第公恐是过者也。过者之弊。其于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5L 页
 事有多不足恤者。常爱王阳明之言。有曰语到快活时。必截然能讱默得。意到发扬时。必翕然能收敛得。喜怒嗜欲蜚腾时。必廓然能消化得。为天下之大勇。此果克治之要法也。向者客座。愚言以俗待公之语。戏之也。此岂实语哉。涉俗之中。有不俗者存焉。其轻重低仰。在我之一心。而惟其正而已。稍涉一毫权谲意思。其弊有不可言矣。公若于此不谓已知已能而回头旋念。则未必无小补矣。
事有多不足恤者。常爱王阳明之言。有曰语到快活时。必截然能讱默得。意到发扬时。必翕然能收敛得。喜怒嗜欲蜚腾时。必廓然能消化得。为天下之大勇。此果克治之要法也。向者客座。愚言以俗待公之语。戏之也。此岂实语哉。涉俗之中。有不俗者存焉。其轻重低仰。在我之一心。而惟其正而已。稍涉一毫权谲意思。其弊有不可言矣。公若于此不谓已知已能而回头旋念。则未必无小补矣。答李士兴书(乙巳)
天学一节。出于切紧之间。而其学异于吾儒貌象。故先入为主。恐其为索隐行怪之归。略以迷见。有所质问于执事及鹿庵。而终未见一字所答。其为高明辈所弃信矣。然事之是非姑舍。有问无答。自非相绝之外。无是事也。何为而至于是耶。惟此一心。不知其迷而不悟。恐或有错。前后略贡愚见。出于血忱。而近来从京外亲知之去来者及或书尺间有所闻见。则以此老汉为惹起事端之一祸首。其言狼藉。而自有此事以后。果然尊尚此学者。自生疑阻。不求此汉之一片心事。而多有疏外之渐。若以此为咎。则朋友间讲问是非。都归虚地。而惟以谀佞相从可矣。天下之义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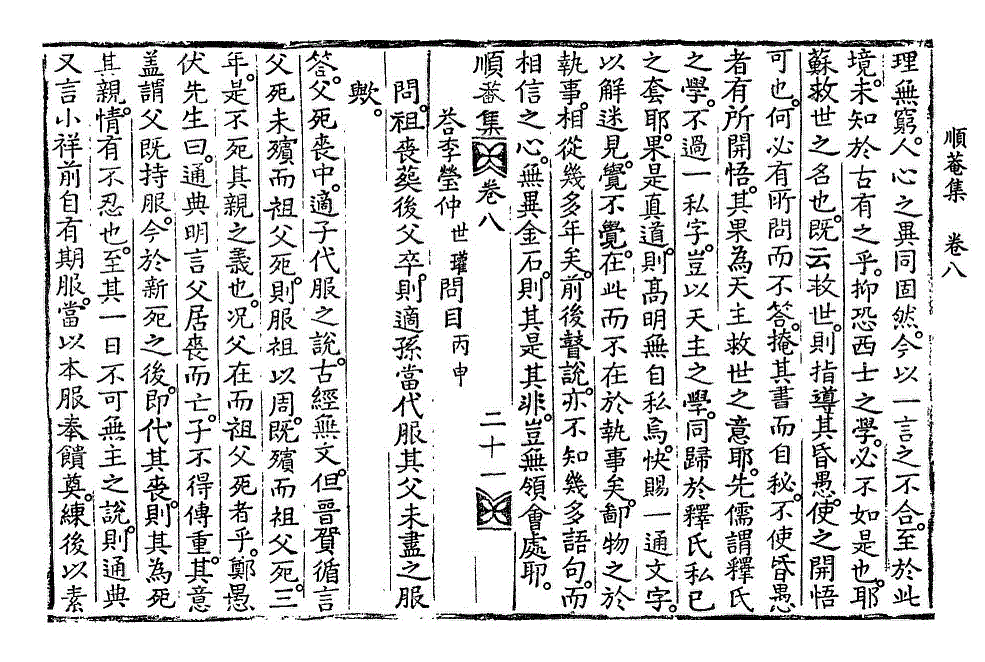 理无穷。人心之异同固然。今以一言之不合。至于此境。未知于古有之乎。抑恐西士之学。必不如是也。耶苏救世之名也。既云救世。则指导其昏愚。使之开悟可也。何必有所问而不答。掩其书而自秘。不使昏愚者有所开悟。其果为天主救世之意耶。先儒谓释氏之学。不过一私字。岂以天主之学。同归于释氏私己之套耶。果是真道。则高明无自私焉。快赐一通文字。以解迷见。觉不觉。在此而不在于执事矣。鄙物之于执事。相从几多年矣。前后瞽说。亦不知几多语句。而相信之心。无异金石。则其是其非。岂无领会处耶。
理无穷。人心之异同固然。今以一言之不合。至于此境。未知于古有之乎。抑恐西士之学。必不如是也。耶苏救世之名也。既云救世。则指导其昏愚。使之开悟可也。何必有所问而不答。掩其书而自秘。不使昏愚者有所开悟。其果为天主救世之意耶。先儒谓释氏之学。不过一私字。岂以天主之学。同归于释氏私己之套耶。果是真道。则高明无自私焉。快赐一通文字。以解迷见。觉不觉。在此而不在于执事矣。鄙物之于执事。相从几多年矣。前后瞽说。亦不知几多语句。而相信之心。无异金石。则其是其非。岂无领会处耶。答李莹仲(世瓘)问目(丙申)
问。祖丧葬后父卒。则适孙当代服其父未尽之服欤。
答。父死丧中。适子代服之说。古经无文。但晋贺循言父死未殡而祖父死。则服祖以周。既殡而祖父死。三年。是不死其亲之义也。况父在而祖父死者乎。郑愚伏先生曰。通典明言父居丧而亡。子不得传重。其意盖谓父既持服。今于新死之后。即代其丧。则其为死其亲。情有不忍也。至其一日不可无主之说。则通典又言小祥前自有期服。当以本服奉馈奠。练后以素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6L 页
 服行之。亦不至阙事云。此说似可为据。近来星湖先生亦言接父服之非。当以不忍死亲一句为宗旨。而求之后来诸儒之说。将无窒碍之患矣。执此论之。其义自见。但今一边知礼之家。皆有代受服之节。至于 肃庙朝代服仁宣王后之服。便成时王之制。此不敢质言。要在商量处之耳。虽不代服。传重正主在于父。摄行葬祭在于己。似不必代服而后。三年之体尤重也。若既从俗代服。则祖主似当改题。恐难行于父丧三年之内。而既告代服之意于祖主。则祖灵已知其然。虽不改题。祝文似当云承重孙孤子某。如依礼不代服。则祝辞似当云摄祀孙孤子某。
服行之。亦不至阙事云。此说似可为据。近来星湖先生亦言接父服之非。当以不忍死亲一句为宗旨。而求之后来诸儒之说。将无窒碍之患矣。执此论之。其义自见。但今一边知礼之家。皆有代受服之节。至于 肃庙朝代服仁宣王后之服。便成时王之制。此不敢质言。要在商量处之耳。虽不代服。传重正主在于父。摄行葬祭在于己。似不必代服而后。三年之体尤重也。若既从俗代服。则祖主似当改题。恐难行于父丧三年之内。而既告代服之意于祖主。则祖灵已知其然。虽不改题。祝文似当云承重孙孤子某。如依礼不代服。则祝辞似当云摄祀孙孤子某。问。承重孙父丧中。当行祖父禫祭欤。
答。祖父之禫。正尊之祭。虽在父丧中。何可废也。若承重代服则无可言。虽不代服。当行之。以备三年有终之礼。练祥禫时。各服其丧之除服。卒事反丧服。自当如礼。若不如此。何以示变除之节耶。
问。备要小祥祝文。或只用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而不用哀慕不宁一句。或以为小心畏忌等八字。亦当用于大祥祝云。或以为不言小祥以后而只言小祥。则不当用于大祥祝云。未知何者为是。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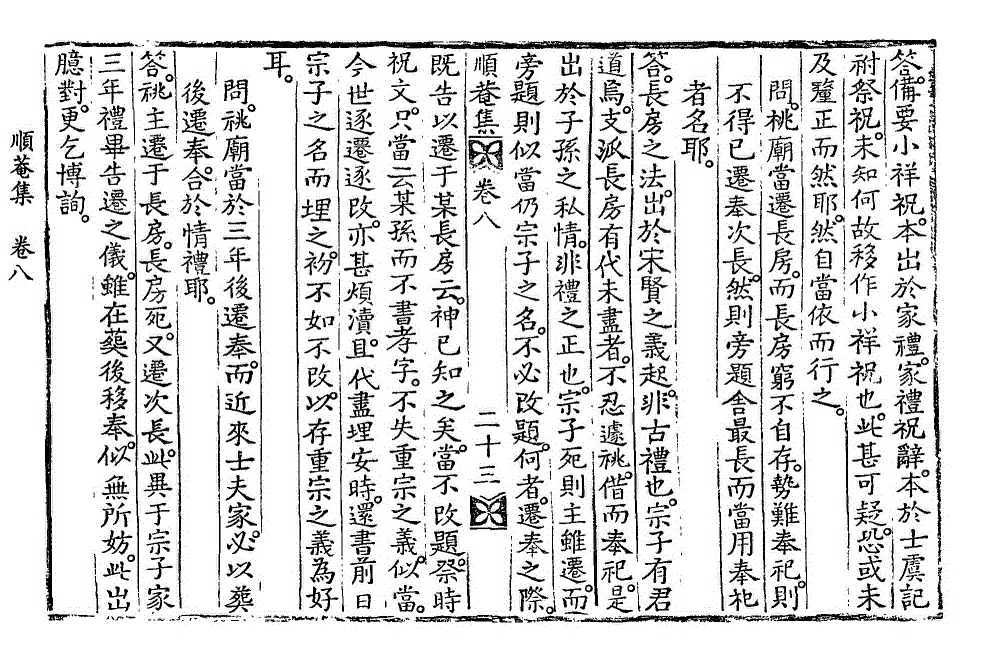 答。备要小祥祝。本出于家礼。家礼祝辞。本于士虞记祔祭祝。未知何故移作小祥祝也。此甚可疑。恐或未及釐正而然耶。然自当依而行之。
答。备要小祥祝。本出于家礼。家礼祝辞。本于士虞记祔祭祝。未知何故移作小祥祝也。此甚可疑。恐或未及釐正而然耶。然自当依而行之。问。祧庙当迁长房。而长房穷不自存。势难奉祀。则不得已迁奉次长。然则旁题舍最长而当用奉祀者名耶。
答。长房之法。出于宋贤之义起。非古礼也。宗子有君道焉。支派长房有代未尽者。不忍遽祧。借而奉祀。是出于子孙之私情。非礼之正也。宗子死则主虽迁。而旁题则似当仍宗子之名。不必改题。何者。迁奉之际。既告以迁于某长房云。神已知之矣。当不改题。祭时祝文。只当云某孙而不书孝字。不失重宗之义。似当。今世逐迁逐改。亦甚烦渎。且代尽埋安时。还书前日宗子之名而埋之。初不如不改。以存重宗之义为好耳。
问。祧庙当于三年后迁奉。而近来士夫家。必以葬后迁奉。合于情礼耶。
答。祧主迁于长房。长房死。又迁次长。此异于宗子家三年礼毕告迁之仪。虽在葬后移奉。似无所妨。此出臆对。更乞博询。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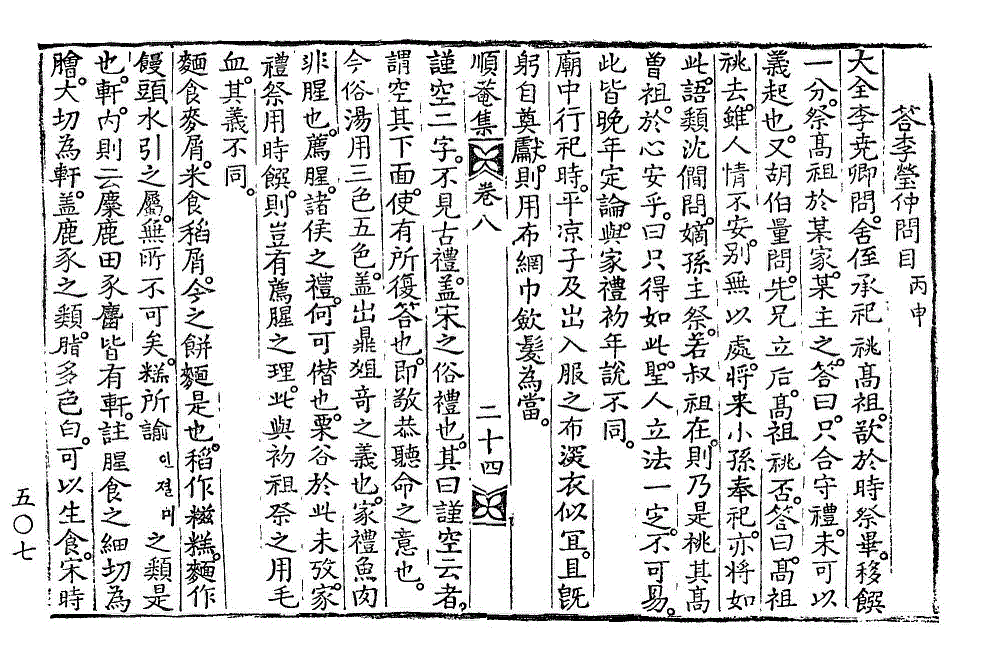 答李莹仲问目(丙申)
答李莹仲问目(丙申)大全李尧卿问。舍侄承祀祧高祖。欲于时祭毕。移馔一分。祭高祖于某家。某主之。答曰。只合守礼。未可以义起也。又胡伯量问。先兄立后。高祖祧否。答曰。高祖祧去。虽人情不安。别无以处。将来小孙奉祀。亦将如此。语类沈僩问。嫡孙主祭。若叔祖在。则乃是祧其高曾祖。于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圣人立法一定。不可易。此皆晚年定论。与家礼初年说不同。
庙中行祀时。平凉子及出入服之布深衣似宜。且既躬自奠献。则用布网巾敛发为当。
谨空二字。不见古礼。盖宋之俗礼也。其曰谨空云者。谓空其下面。使有所复答也。即敬恭听命之意也。
今俗汤用三色五色。盖出鼎俎奇之义也。家礼鱼肉非腥也。荐腥。诸侯之礼。何可僭也。栗谷于此未考。家礼祭用时馔。则岂有荐腥之理。此与初祖祭之用毛血。其义不同。
面食麦屑。米食稻屑。今之饼面是也。稻作糍糕。面作馒头水引之属。无所不可矣。糕所谕(인졀미)之类是也。轩。内则云麋鹿田豕麇皆有轩。注腥食之细切为脍。大切为轩。盖鹿豕之类。脂多色白。可以生食。宋时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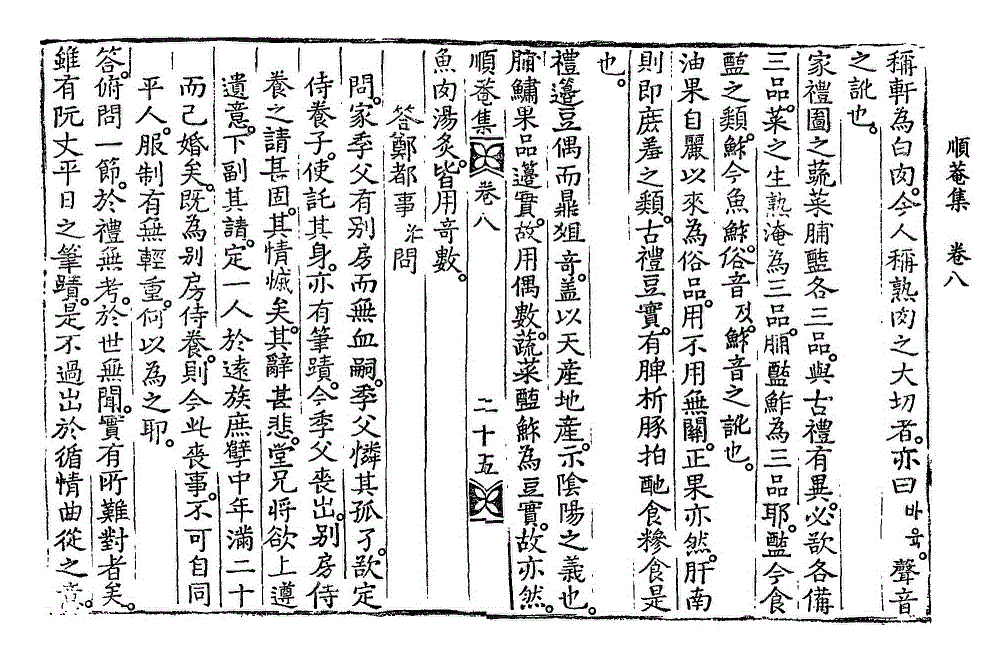 称轩为白肉。今人称熟肉之大切者。亦曰(바육)。声音之讹也。
称轩为白肉。今人称熟肉之大切者。亦曰(바육)。声音之讹也。家礼图之蔬菜脯醢各三品。与古礼有异。必欲各备三品。菜之生熟淹为三品。脯醢鲊为三品耶。醢今食醢之类。鲊今鱼鲊。俗音(젓)。鲊音之讹也。
油果自丽以来为俗品。用不用无关。正果亦然。肝南则即庶羞之类。古礼豆实。有脾析豚拍酏食糁食是也。
礼笾豆偶而鼎俎奇。盖以天产地产。示阴阳之义也。脯鱐果品笾实。故用偶数。蔬菜醢鲊为豆实。故亦然。鱼肉汤炙。皆用奇数。
答郑都事(𣲚)问
问。家季父有别房而无血嗣。季父怜其孤孑。欲定侍养子。使托其身。亦有笔迹。今季父丧出。别房侍养之请甚固。其情戚矣。其辞甚悲。堂兄将欲上遵遗意。下副其请。定一人于远族庶孽中年满二十而已婚矣。既为别房侍养。则今此丧事。不可自同平人。服制有无轻重。何以为之耶。
答。俯问一节。于礼无考。于世无闻。实有所难对者矣。虽有阮丈平日之笔迹。是不过出于循情曲从之意。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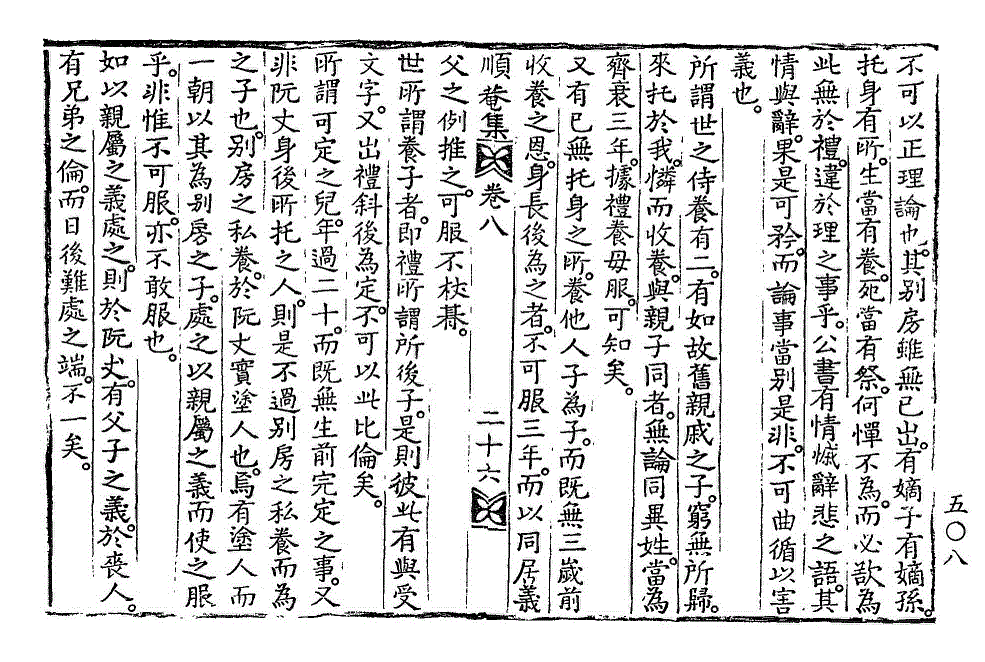 不可以正理论也。其别房虽无己出。有嫡子有嫡孙。托身有所。生当有养。死当有祭。何惮不为。而必欲为此无于礼。违于理之事乎。公书有情戚辞悲之语。其情与辞。果是可矜。而论事当别是非。不可曲循以害义也。
不可以正理论也。其别房虽无己出。有嫡子有嫡孙。托身有所。生当有养。死当有祭。何惮不为。而必欲为此无于礼。违于理之事乎。公书有情戚辞悲之语。其情与辞。果是可矜。而论事当别是非。不可曲循以害义也。所谓世之侍养有二。有如故旧亲戚之子。穷无所归。来托于我。怜而收养。与亲子同者。无论同异姓。当为齐衰三年。据礼养母服。可知矣。
又有己无托身之所。养他人子为子。而既无三岁前收养之恩。身长后为之者。不可服三年。而以同居义父之例推之。可服不杖期。
世所谓养子者。即礼所谓所后子。是则彼此有与受文字。又出礼斜后为定。不可以此比伦矣。
所谓可定之儿。年过二十。而既无生前完定之事。又非阮丈身后所托之人。则是不过别房之私养而为之子也。别房之私养。于阮丈实涂人也。焉有涂人而一朝以其为别房之子。处之以亲属之义而使之服乎。非惟不可服。亦不敢服也。
如以亲属之义处之。则于阮丈。有父子之义。于丧人。有兄弟之伦。而日后难处之端。不一矣。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9H 页
 窃想此事。出于闺房执拗固请。势有不已。则但使别房子之而已。不使干涉于嫡家。而若使出入丧侧。则不过素服素带。以终别房脱服之时。日后别房死后。不过服侍养服不杖期矣。迷见如此。幸又广询。毋致人唇舌也。
窃想此事。出于闺房执拗固请。势有不已。则但使别房子之而已。不使干涉于嫡家。而若使出入丧侧。则不过素服素带。以终别房脱服之时。日后别房死后。不过服侍养服不杖期矣。迷见如此。幸又广询。毋致人唇舌也。答黄耳叟(德吉)书(辛丑)
向也伯季联袂委访于寂寞之滨。兰情蕙思。殆犹难忘。伯氏之来。相与论说多矣。无论中否。慰满即深。见君书意。既非世俗边幅循例之言而出于实心。是何等欢喜消息耶。后学所业。惟在程朱平正门路。明明白白。坦坦荡荡。苟能讲求而体行。则实易为力矣。大抵为学之方。必先博文。必贵自得。然欲其博文。则多闻慎言。多见慎行。审问明辨。多识畜德之谓也。非若世之搜求隐僻之事。钩摘奇异之说。誇多斗靡。以为口耳记诵之资者也。欲其自得。则体之于心。验之于身。真积力久。自然贯通之谓也。非若世之穷格未到。意虑横生。偶有所见。自以为发前人之未发。至于诬经离道而不知止者也。故曰进德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主一无适之谓敬。盖致知则博文之事也。敬之之久。则自然有得于心也。主一无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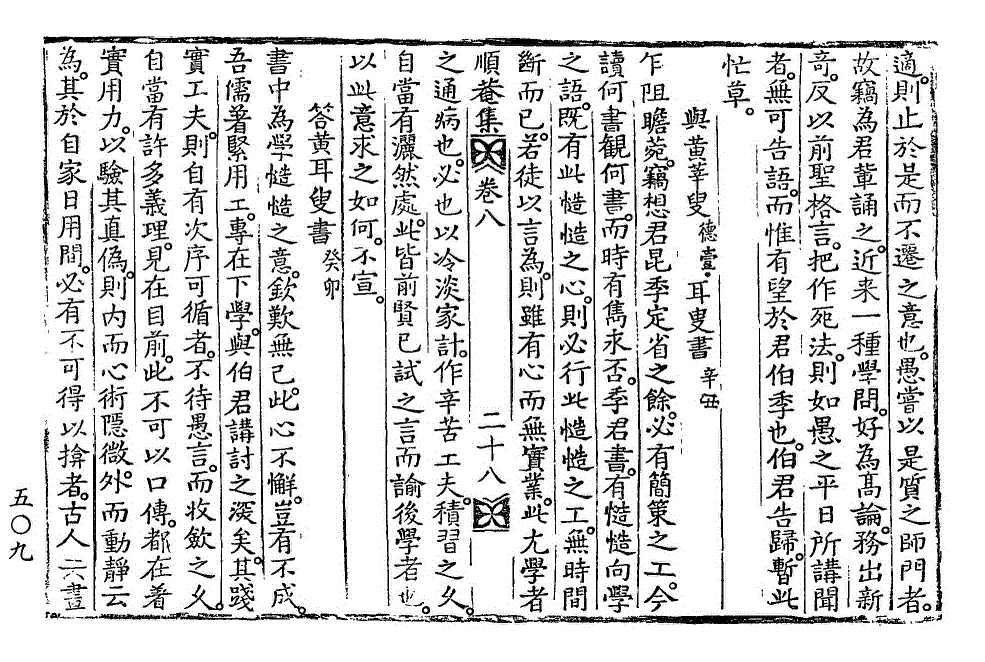 适。则止于是而不迁之意也。愚尝以是质之师门者。故窃为君辈诵之。近来一种学问。好为高论。务出新奇。反以前圣格言。把作死法。则如愚之平日所讲闻者。无可告语。而惟有望于君伯季也。伯君告归。暂此忙草。
适。则止于是而不迁之意也。愚尝以是质之师门者。故窃为君辈诵之。近来一种学问。好为高论。务出新奇。反以前圣格言。把作死法。则如愚之平日所讲闻者。无可告语。而惟有望于君伯季也。伯君告归。暂此忙草。与黄莘叟(德壹),耳叟书(辛丑)
乍阻瞻菀。窃想君昆季定省之馀。必有简策之工。今读何书观何书。而时有隽永否。季君书。有慥慥向学之语。既有此慥慥之心。则必行此慥慥之工。无时间断而已。若徒以言为。则虽有心而无实业。此尤学者之通病也。必也以冷淡家计。作辛苦工夫。积习之久。自当有洒然处。此皆前贤已试之言而谕后学者也。以此意求之如何。不宣。
答黄耳叟书(癸卯)
书中为学慥慥之意。钦叹无已。此心不懈。岂有不成。吾儒着紧用工。专在下学。与伯君讲讨之深矣。其践实工夫。则自有次序可循者。不待愚言。而收敛之久。自当有许多义理。见在目前。此不可以口传。都在着实用力。以验其真伪。则内而心术隐微。外而动静云为。其于自家日用间。必有不可得以掩者。古人云昼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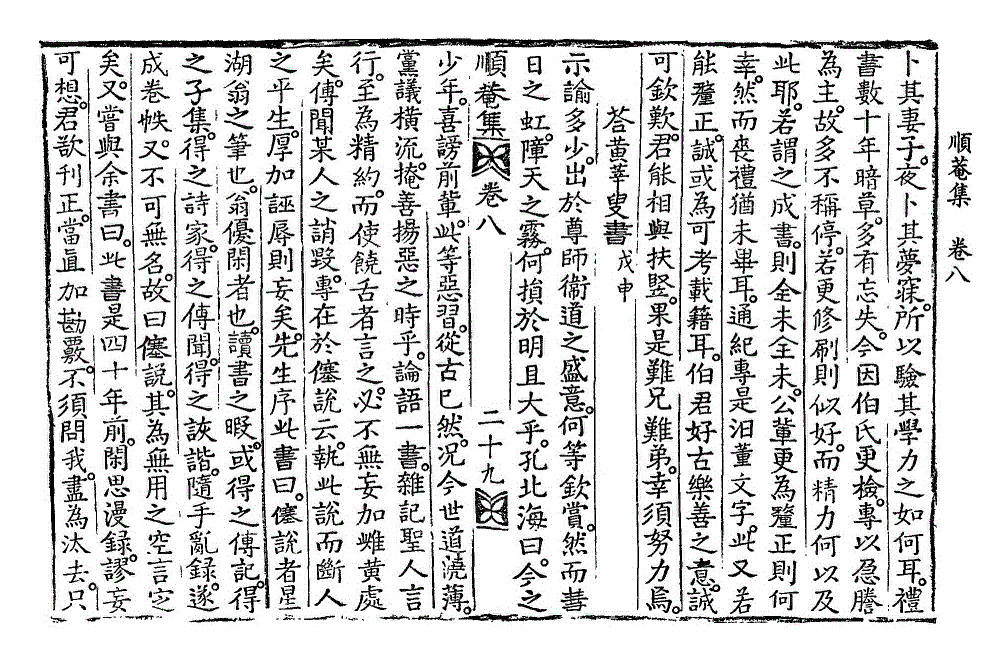 卜其妻子。夜卜其梦寐。所以验其学力之如何耳。礼书数十年暗草。多有忘失。今因伯氏更检。专以急誊为主。故多不称停。若更修刷则似好。而精力何以及此耶。若谓之成书。则全未全未。公辈更为釐正则何幸。然而丧礼犹未毕耳。通纪专是汨董文字。此又若能釐正。诚或为可考载籍耳。伯君好古乐善之意。诚可钦叹。君能相与扶竖。果是难兄难弟。幸须努力焉。
卜其妻子。夜卜其梦寐。所以验其学力之如何耳。礼书数十年暗草。多有忘失。今因伯氏更检。专以急誊为主。故多不称停。若更修刷则似好。而精力何以及此耶。若谓之成书。则全未全未。公辈更为釐正则何幸。然而丧礼犹未毕耳。通纪专是汨董文字。此又若能釐正。诚或为可考载籍耳。伯君好古乐善之意。诚可钦叹。君能相与扶竖。果是难兄难弟。幸须努力焉。答黄莘叟书(戊申)
示谕多少。出于尊师卫道之盛意。何等钦赏。然而彗日之虹。障天之雾。何损于明且大乎。孔北海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此等恶习。从古已然。况今世道浇薄。党议横流。掩善扬恶之时乎。论语一书。杂记圣人言行。至为精约。而使饶舌者言之。必不无妄加雌黄处矣。传闻某人之诮毁。专在于僿说云。执此说而断人之平生。厚加诬辱则妄矣。先生序此书曰。僿说者星湖翁之笔也。翁优闲者也。读书之暇。或得之传记。得之子集。得之诗家。得之传闻。得之诙谐。随手乱录。遂成卷帙。又不可无名。故曰僿说。其为无用之空言定矣。又尝与余书曰。此书是四十年前。闲思漫录。谬妄可想。君欲刊正。当直加勘覈。不须问我。尽为汰去。只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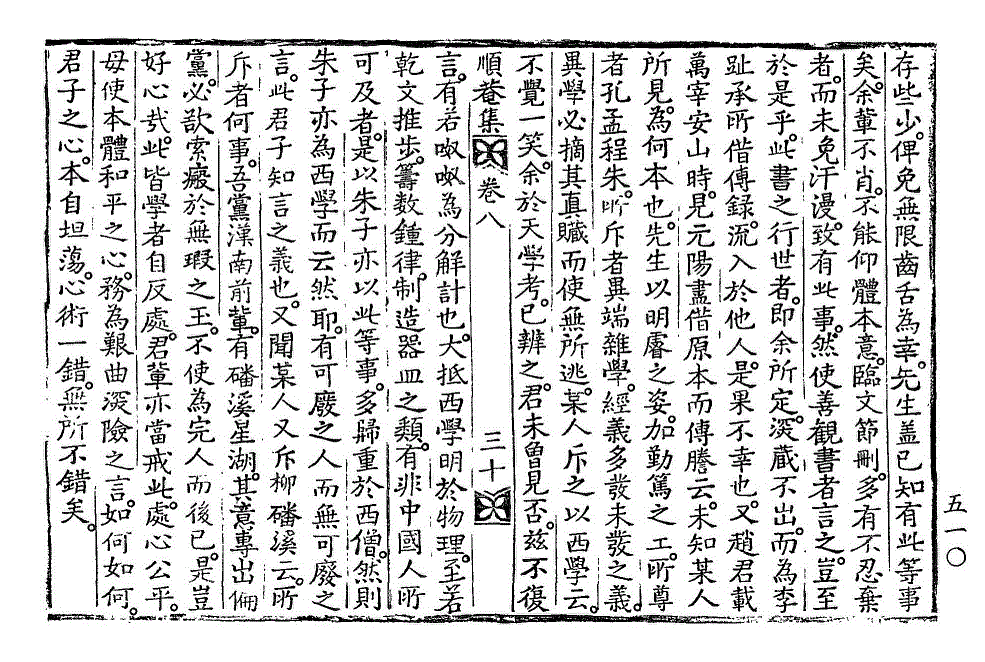 存些少。俾免无限齿舌为幸。先生盖已知有此等事矣。余辈不肖。不能仰体本意。临文节删。多有不忍弃者。而未免汗漫。致有此事。然使善观书者言之。岂至于是乎。此书之行世者。即余所定。深藏不出。而为李趾承所借传录。流入于他人。是果不幸也。又赵君载万宰安山时。见元阳尽借原本而传誊云。未知某人所见。为何本也。先生以明睿之姿。加勤笃之工。所尊者孔孟程朱。所斥者异端杂学。经义多发未发之义。异学必摘其真赃而使无所逃。某人斥之以西学云。不觉一笑。余于天学考。已辨之。君未曾见否。玆不复言。有若呶呶为分解计也。大抵西学明于物理。至若乾文推步。筹数钟律。制造器皿之类。有非中国人所可及者。是以朱子亦以此等事。多归重于西僧。然则朱子亦为西学而云然耶。有可废之人而无可废之言。此君子知言之义也。又闻某人又斥柳磻溪云。所斥者何事。吾党汉南前辈。有磻溪星湖。其意专出偏党。必欲索瘢于无瑕之玉。不使为完人而后已。是岂好心哉。此皆学者自反处。君辈亦当戒此。处心公平。毋使本体和平之心。务为艰曲深险之言。如何如何。君子之心。本自坦荡。心术一错。无所不错矣。
存些少。俾免无限齿舌为幸。先生盖已知有此等事矣。余辈不肖。不能仰体本意。临文节删。多有不忍弃者。而未免汗漫。致有此事。然使善观书者言之。岂至于是乎。此书之行世者。即余所定。深藏不出。而为李趾承所借传录。流入于他人。是果不幸也。又赵君载万宰安山时。见元阳尽借原本而传誊云。未知某人所见。为何本也。先生以明睿之姿。加勤笃之工。所尊者孔孟程朱。所斥者异端杂学。经义多发未发之义。异学必摘其真赃而使无所逃。某人斥之以西学云。不觉一笑。余于天学考。已辨之。君未曾见否。玆不复言。有若呶呶为分解计也。大抵西学明于物理。至若乾文推步。筹数钟律。制造器皿之类。有非中国人所可及者。是以朱子亦以此等事。多归重于西僧。然则朱子亦为西学而云然耶。有可废之人而无可废之言。此君子知言之义也。又闻某人又斥柳磻溪云。所斥者何事。吾党汉南前辈。有磻溪星湖。其意专出偏党。必欲索瘢于无瑕之玉。不使为完人而后已。是岂好心哉。此皆学者自反处。君辈亦当戒此。处心公平。毋使本体和平之心。务为艰曲深险之言。如何如何。君子之心。本自坦荡。心术一错。无所不错矣。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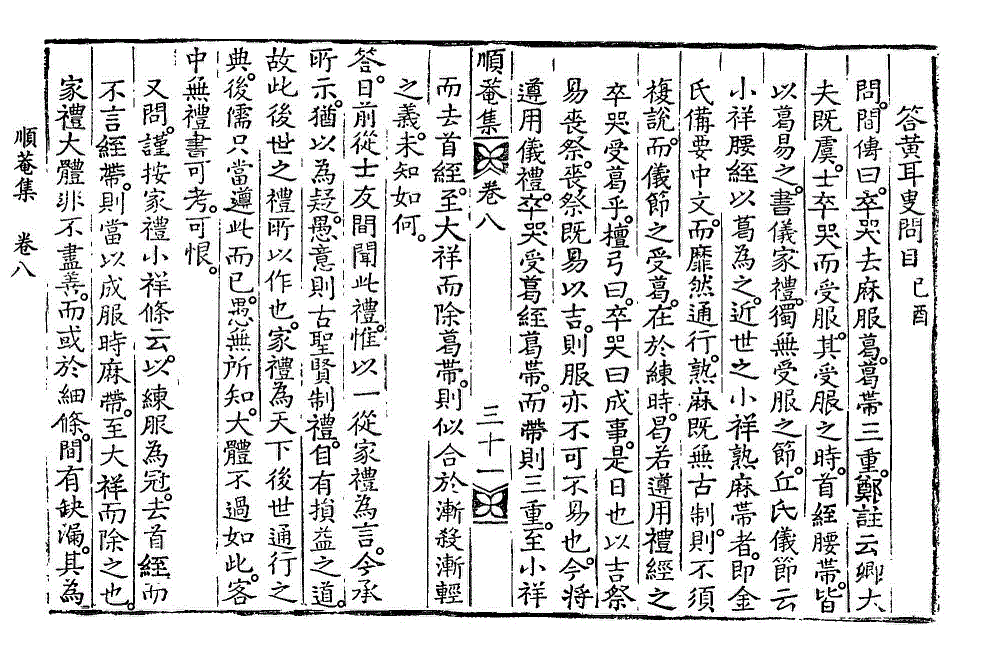 答黄耳叟问目(己酉)
答黄耳叟问目(己酉)问。间传曰。卒哭去麻服葛。葛带三重。郑注云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时。首绖腰带。皆以葛易之。书仪家礼。独无受服之节。丘氏仪节云小祥腰绖以葛为之。近世之小祥熟麻带者。即金氏备要中文。而靡然通行。熟麻既无古制。则不须复说。而仪节之受葛。在于练时。曷若遵用礼经之卒哭受葛乎。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丧祭既易以吉。则服亦不可不易也。今将遵用仪礼。卒哭受葛绖葛带。而带则三重。至小祥而去首绖。至大祥而除葛带。则似合于渐杀渐轻之义。未知如何。
答。日前从士友间闻此礼。惟以一从家礼为言。今承所示。犹以为疑。愚意则古圣贤制礼。自有损益之道。故此后世之礼所以作也。家礼为天下后世通行之典。后儒只当遵此而已。愚无所知。大体不过如此。客中无礼书可考。可恨。
又问。谨按家礼小祥条云。以练服为冠。去首绖而不言绖带。则当以成服时麻带。至大祥而除之也。家礼大体非不尽善。而或于细条。间有缺漏。其为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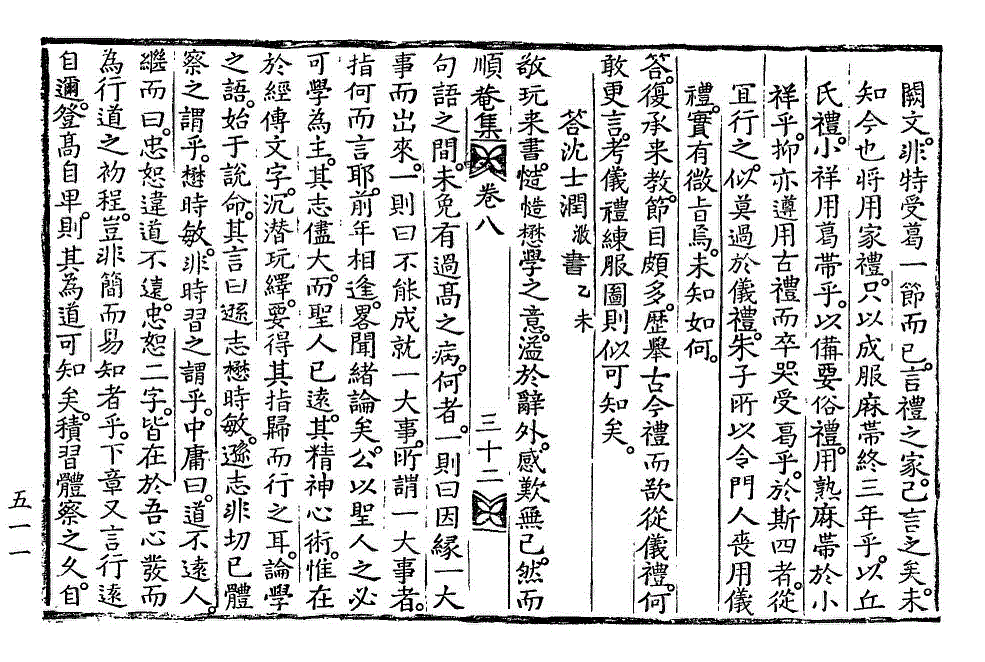 阙文。非特受葛一节而已。言礼之家。已言之矣。未知今也将用家礼。只以成服麻带终三年乎。以丘氏礼。小祥用葛带乎。以备要俗礼。用熟麻带于小祥乎。抑亦遵用古礼而卒哭受葛乎。于斯四者。从宜行之。似莫过于仪礼。朱子所以令门人丧用仪礼。实有微旨焉。未知如何。
阙文。非特受葛一节而已。言礼之家。已言之矣。未知今也将用家礼。只以成服麻带终三年乎。以丘氏礼。小祥用葛带乎。以备要俗礼。用熟麻带于小祥乎。抑亦遵用古礼而卒哭受葛乎。于斯四者。从宜行之。似莫过于仪礼。朱子所以令门人丧用仪礼。实有微旨焉。未知如何。答。复承来教。节目颇多。历举古今礼而欲从仪礼。何敢更言。考仪礼练服图则似可知矣。
答沈士润(浟)书(乙未)
敬玩来书。慥慥懋学之意。溢于辞外。感叹无已。然而句语之间。未免有过高之病。何者。一则曰因缘一大事而出来。一则曰不能成就一大事。所谓一大事者。指何而言耶。前年相逢。略闻绪论矣。公以圣人之必可学为主。其志尽大。而圣人已远。其精神心术。惟在于经传文字。沉潜玩绎。要得其指归而行之耳。论学之语。始于说命。其言曰逊志懋时敏。逊志非切己体察之谓乎。懋时敏。非时习之谓乎。中庸曰。道不远人。继而曰。忠恕违道不远。忠恕二字。皆在于吾心发而为行道之初程。岂非简而易知者乎。下章又言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则其为道可知矣。积习体察之久。自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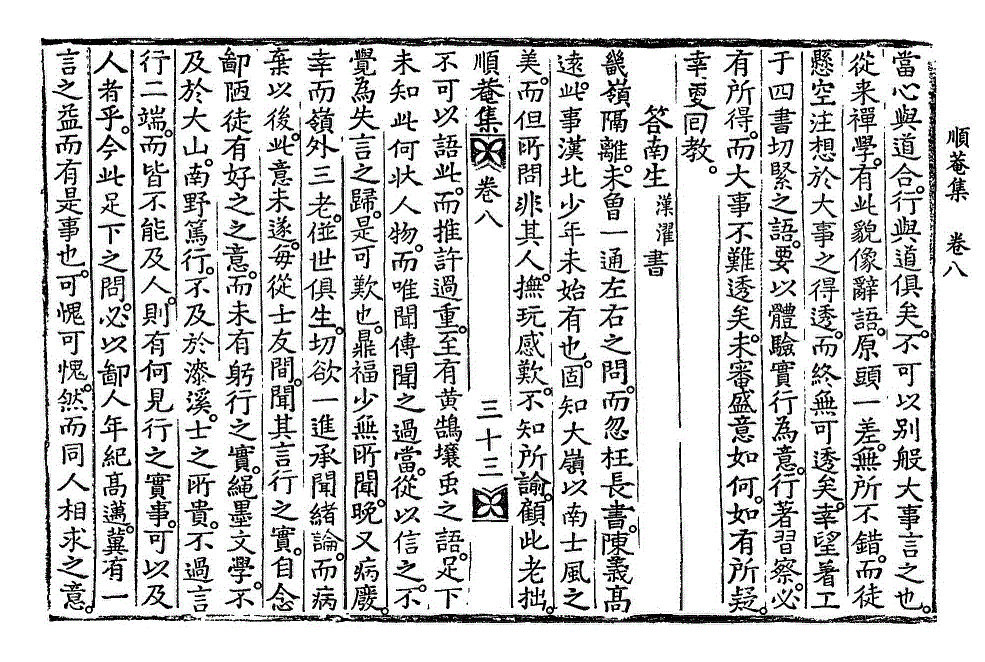 当心与道合。行与道俱矣。不可以别般大事言之也。从来禅学。有此貌像辞语。原头一差。无所不错。而徒悬空注想于大事之得透。而终无可透矣。幸望着工于四书切紧之语。要以体验实行为意。行著习察。必有所得。而大事不难透矣。未审盛意如何。如有所疑。幸更回教。
当心与道合。行与道俱矣。不可以别般大事言之也。从来禅学。有此貌像辞语。原头一差。无所不错。而徒悬空注想于大事之得透。而终无可透矣。幸望着工于四书切紧之语。要以体验实行为意。行著习察。必有所得。而大事不难透矣。未审盛意如何。如有所疑。幸更回教。答南生(汉濯)书
畿岭隔离。未曾一通左右之问。而忽枉长书。陈义高远。此事汉北少年未始有也。固知大岭以南士风之美。而但所问非其人。抚玩感叹。不知所谕。顾此老拙。不可以语此。而推许过重。至有黄鹄壤虫之语。足下未知此何状人物。而唯闻传闻之过当。从以信之。不觉为失言之归。是可叹也。鼎福少无所闻。晚又病废。幸而岭外三老。并世俱生。切欲一进承闻绪论。而病弃以后。此意未遂。每从士友间。闻其言行之实。自念鄙陋徒有好之之意。而未有躬行之实。绳墨文学。不及于大山。南野笃行。不及于漆溪。士之所贵。不过言行二端。而皆不能及人。则有何见行之实事。可以及人者乎。今此足下之问。必以鄙人年纪高迈。冀有一言之益而有是事也。可愧可愧。然而同人相求之意。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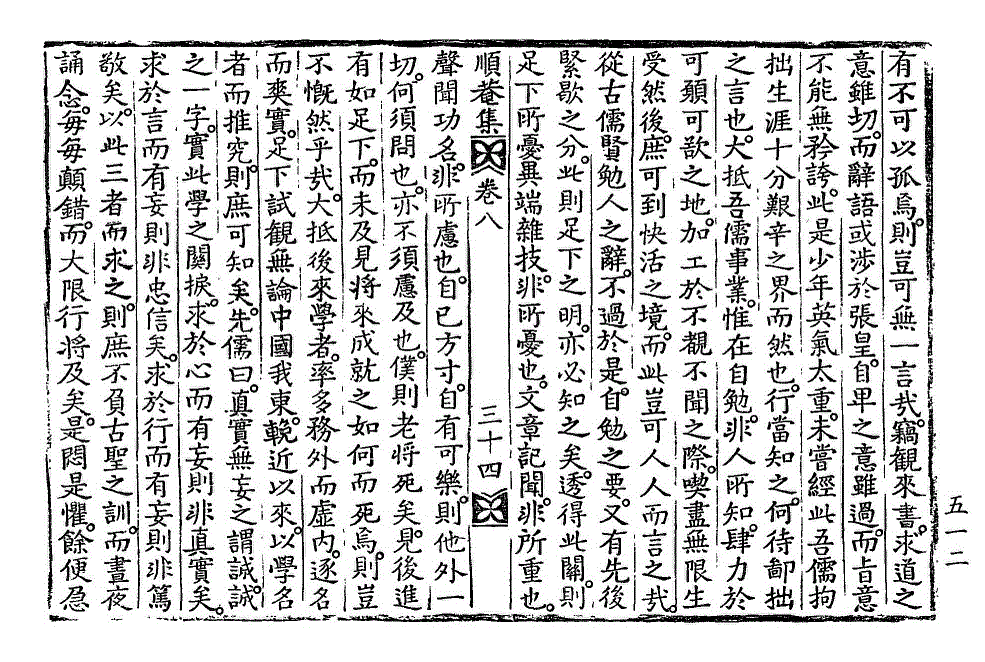 有不可以孤焉。则岂可无一言哉。窃观来书。求道之意虽切。而辞语或涉于张皇。自卑之意虽过。而旨意不能无矜誇。此是少年英气太重。未尝经此吾儒拘拙生涯十分艰辛之界而然也。行当知之。何待鄙拙之言也。大抵吾儒事业。惟在自勉。非人所知。肆力于可愿可欲之地。加工于不睹不闻之际。吃尽无限生受然后。庶可到快活之境。而此岂可人人而言之哉。从古儒贤勉人之辞。不过于是。自勉之要。又有先后紧歇之分。此则足下之明。亦必知之矣。透得此关。则足下所忧异端杂技。非所忧也。文章记闻。非所重也。声闻功名。非所虑也。自己方寸。自有可乐。则他外一切。何须问也。亦不须虑及也。仆则老将死矣。见后进有如足下。而未及见将来成就之如何而死焉。则岂不慨然乎哉。大抵后来学者。率多务外而虚内。逐名而爽实。足下试观无论中国我东。挽近以来。以学名者而推究。则庶可知矣。先儒曰。真实无妄之谓诚。诚之一字。实此学之关捩。求于心而有妄则非真实矣。求于言而有妄则非忠信矣。求于行而有妄则非笃敬矣。以此三者而求之。则庶不负古圣之训。而昼夜诵念。每每颠错。而大限行将及矣。是闷是惧。馀便急
有不可以孤焉。则岂可无一言哉。窃观来书。求道之意虽切。而辞语或涉于张皇。自卑之意虽过。而旨意不能无矜誇。此是少年英气太重。未尝经此吾儒拘拙生涯十分艰辛之界而然也。行当知之。何待鄙拙之言也。大抵吾儒事业。惟在自勉。非人所知。肆力于可愿可欲之地。加工于不睹不闻之际。吃尽无限生受然后。庶可到快活之境。而此岂可人人而言之哉。从古儒贤勉人之辞。不过于是。自勉之要。又有先后紧歇之分。此则足下之明。亦必知之矣。透得此关。则足下所忧异端杂技。非所忧也。文章记闻。非所重也。声闻功名。非所虑也。自己方寸。自有可乐。则他外一切。何须问也。亦不须虑及也。仆则老将死矣。见后进有如足下。而未及见将来成就之如何而死焉。则岂不慨然乎哉。大抵后来学者。率多务外而虚内。逐名而爽实。足下试观无论中国我东。挽近以来。以学名者而推究。则庶可知矣。先儒曰。真实无妄之谓诚。诚之一字。实此学之关捩。求于心而有妄则非真实矣。求于言而有妄则非忠信矣。求于行而有妄则非笃敬矣。以此三者而求之。则庶不负古圣之训。而昼夜诵念。每每颠错。而大限行将及矣。是闷是惧。馀便急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3H 页
 暂此。强疾草候。
暂此。强疾草候。答南宗伯(汉朝)书(丙午)
大山已颓。南野荒芜。而吾道益孤。虽未有生时相从之乐。而南北相望。意向不少。徒有耿耿之怀。又闻漆溪之丧。令人气短。此亦从此逝矣。而未死之前。怆怀徒切。今见盛书。有若以仆为可语以此学者。此公之过许而未免为失言也。渠事渠知。仆当索言之。仆天赋残尪。早罹奇疾。六十年鬼窟生涯。有何学问之可言欤。但此降衷之性。圣愚一样。故虽欲振拔。而少无师友之助。妄奔走于多歧。年二十五。始得性理大全。读过三冬。遂知吾儒门路。而疾病缠身。惟常抚卷兴喟而已。不曾施实下之工。常常歉恨。三十五岁。始谒星湖。颇蒙印可。因亦自信。而旋出世路。六年奔汨。遭艰病呕血。永作癃废之物。至于今耳。若谓之好此学则可。谓之知此学则不可矣。才分短劣。而常谓孔门教人。不过孝经论语。此二书。皆于下学有依据处言之。是以性与天道。虽以子贡之明悟。有不得闻也。下学之久。涵养德性。心气灵明。上达一事。随其工夫所到而得之有浅深矣。凡为学。当观时弊。今之学者。大抵不屑于下学。而徒役心于性命理气四七之辨。今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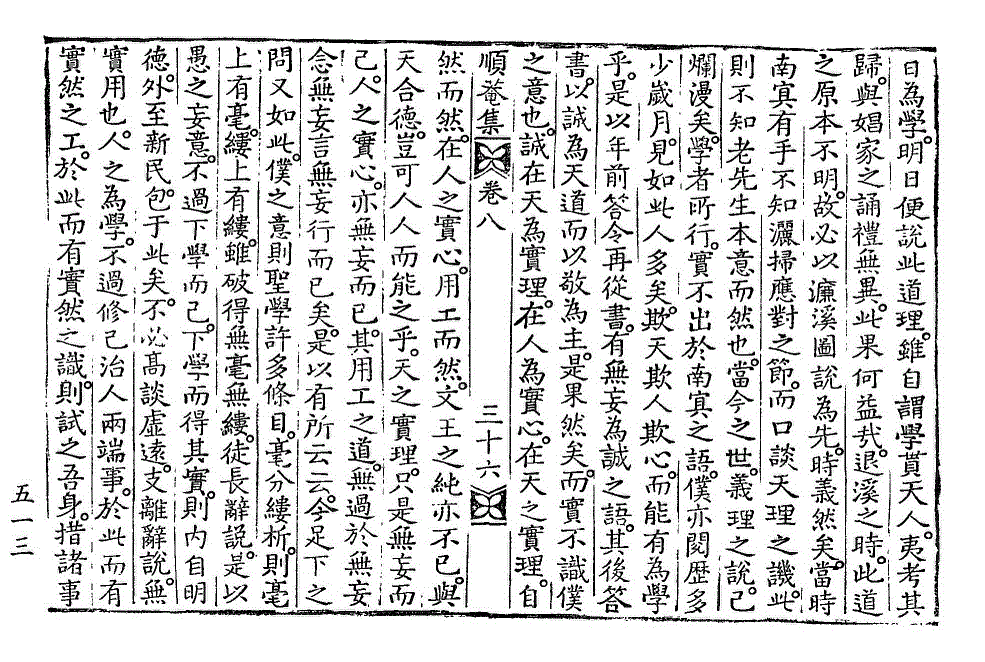 日为学。明日便说此道理。虽自谓学贯天人。夷考其归。与娼家之诵礼无异。此果何益哉。退溪之时。此道之原本不明。故必以濂溪图说为先。时义然矣。当时南冥有手不知洒扫应对之节。而口谈天理之讥。此则不知老先生本意而然也。当今之世。义理之说。已烂漫矣。学者所行。实不出于南冥之语。仆亦阅历多少岁月。见如此人多矣。欺天欺人欺心。而能有为学乎。是以年前答令再从书。有无妄为诚之语。其后答书。以诚为天道而以敬为主。是果然矣。而实不识仆之意也。诚在天为实理。在人为实心。在天之实理。自然而然。在人之实心。用工而然。文王之纯亦不已。与天合德。岂可人人而能之乎。天之实理。只是无妄而已。人之实心。亦无妄而已。其用工之道。无过于无妄念无妄言无妄行而已矣。是以有所云云。今足下之问又如此。仆之意则圣学许多条目。毫分缕析。则毫上有毫。缕上有缕。虽破得无毫无缕。徒长辞说。是以愚之妄意。不过下学而已。下学而得其实。则内自明德。外至新民。包于此矣。不必高谈虚远。支离辞说。无实用也。人之为学。不过修己治人两端事。于此而有实然之工。于此而有实然之识。则试之吾身。措诸事
日为学。明日便说此道理。虽自谓学贯天人。夷考其归。与娼家之诵礼无异。此果何益哉。退溪之时。此道之原本不明。故必以濂溪图说为先。时义然矣。当时南冥有手不知洒扫应对之节。而口谈天理之讥。此则不知老先生本意而然也。当今之世。义理之说。已烂漫矣。学者所行。实不出于南冥之语。仆亦阅历多少岁月。见如此人多矣。欺天欺人欺心。而能有为学乎。是以年前答令再从书。有无妄为诚之语。其后答书。以诚为天道而以敬为主。是果然矣。而实不识仆之意也。诚在天为实理。在人为实心。在天之实理。自然而然。在人之实心。用工而然。文王之纯亦不已。与天合德。岂可人人而能之乎。天之实理。只是无妄而已。人之实心。亦无妄而已。其用工之道。无过于无妄念无妄言无妄行而已矣。是以有所云云。今足下之问又如此。仆之意则圣学许多条目。毫分缕析。则毫上有毫。缕上有缕。虽破得无毫无缕。徒长辞说。是以愚之妄意。不过下学而已。下学而得其实。则内自明德。外至新民。包于此矣。不必高谈虚远。支离辞说。无实用也。人之为学。不过修己治人两端事。于此而有实然之工。于此而有实然之识。则试之吾身。措诸事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4H 页
 业。无不可矣。我东学问。箕教尚矣无徵。自新罗通聘上国以后。始有文献。而中国此时当南北朝隋唐之际。惟尚文词。是以罗之选士。以文选试之。则槩可知矣。自胜国之末。益斋,牧隐游宦大国。得程朱性理之说而归。于是而吾东学者。果彬彬然也。 圣祖开国。朝不换班。市不易肆。可谓尧舜禅让。而亲试旧都士民。三日设场。无一人呈券。遂有百年停举之 教。胜国名节之卓然。盖出于学问而然也。君子成德之名。名节是成德中一事。则不必单举。而足下观今世道。名节果何如耶。出世者惟知仕宦。应举者惟知被选。中间许多羞闷之事。不一而足。自以为能。若有一毫人心。腼然无耻。岂至于是乎。愿以此意布告于岭中少辈如何。愚常言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各以救时之弊也。若欲救今之弊。非伯夷不可。危行言逊。各有其宜。至于自己处心。必以伯夷为师。然后庶几无愧矣。未知此意如何。岭中三老屹然为后生之前茅。今焉已矣。芝焚蕙叹。到此益切。前辈沦落。虽甚忧叹。吾儒一脉。专恃岭中后辈。岂无继此而起者乎。闻郑斯文宗鲁有斯文之托。岂胜欣慰。近来安否。果何如耶。带疾呼倩。不宣。
业。无不可矣。我东学问。箕教尚矣无徵。自新罗通聘上国以后。始有文献。而中国此时当南北朝隋唐之际。惟尚文词。是以罗之选士。以文选试之。则槩可知矣。自胜国之末。益斋,牧隐游宦大国。得程朱性理之说而归。于是而吾东学者。果彬彬然也。 圣祖开国。朝不换班。市不易肆。可谓尧舜禅让。而亲试旧都士民。三日设场。无一人呈券。遂有百年停举之 教。胜国名节之卓然。盖出于学问而然也。君子成德之名。名节是成德中一事。则不必单举。而足下观今世道。名节果何如耶。出世者惟知仕宦。应举者惟知被选。中间许多羞闷之事。不一而足。自以为能。若有一毫人心。腼然无耻。岂至于是乎。愿以此意布告于岭中少辈如何。愚常言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各以救时之弊也。若欲救今之弊。非伯夷不可。危行言逊。各有其宜。至于自己处心。必以伯夷为师。然后庶几无愧矣。未知此意如何。岭中三老屹然为后生之前茅。今焉已矣。芝焚蕙叹。到此益切。前辈沦落。虽甚忧叹。吾儒一脉。专恃岭中后辈。岂无继此而起者乎。闻郑斯文宗鲁有斯文之托。岂胜欣慰。近来安否。果何如耶。带疾呼倩。不宣。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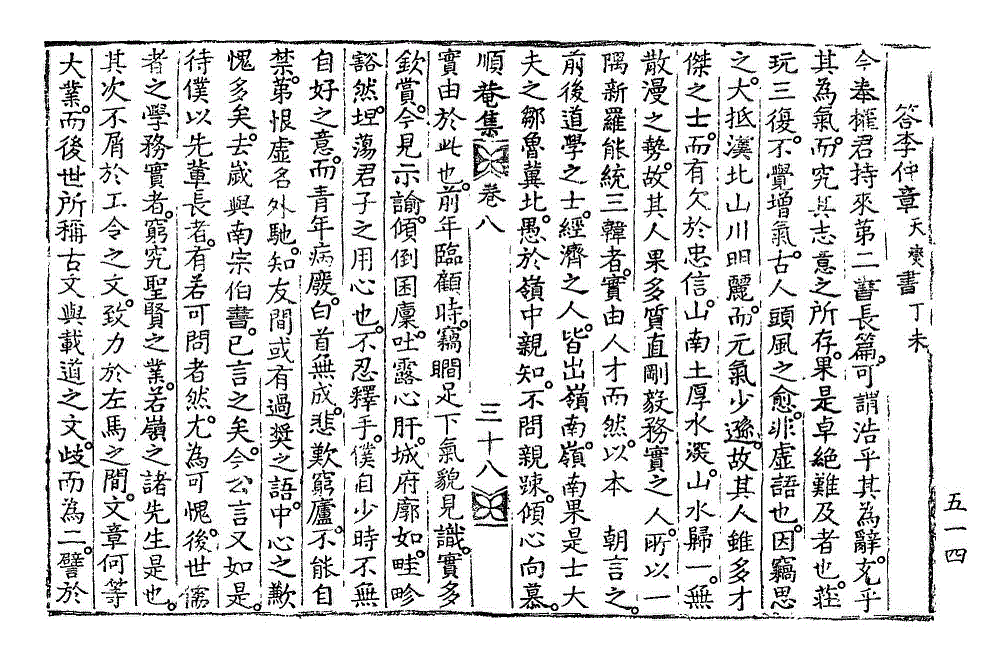 答李仲章(天燮)书(丁未)
答李仲章(天燮)书(丁未)今奉权君持来第二书长篇。可谓浩乎其为辞。充乎其为气。而究其志意之所存。果是卓绝难及者也。庄玩三复。不觉增气。古人头风之愈。非虚语也。因窃思之。大抵汉北山川明丽。而元气少逊。故其人虽多才杰之士。而有欠于忠信。山南土厚水深。山水归一。无散漫之势。故其人果多质直刚毅务实之人。所以一隅新罗能统三韩者。实由人才而然。以本 朝言之。前后道学之士。经济之人。皆出岭南。岭南果是士大夫之邹鲁冀北。愚于岭中亲知。不问亲疏。倾心向慕。实由于此也。前年临顾时。窃瞷足下气貌见识。实多钦赏。今见示谕。倾倒囷廪。吐露心肝。城府廓如。畦畛豁然。坦荡君子之用心也。不忍释手。仆自少时不无自好之意。而青年病废。白首无成。悲叹穷庐。不能自禁。第恨虚名外驰。知友间或有过奖之语。中心之歉愧多矣。去岁与南宗伯书。已言之矣。今公言又如是。待仆以先辈长者。有若可问者然。尤为可愧。后世儒者之学务实者。穷究圣贤之业。若岭之诸先生是也。其次不屑于工令之文。致力于左马之间。文章何等大业。而后世所称古文与载道之文。歧而为二。譬于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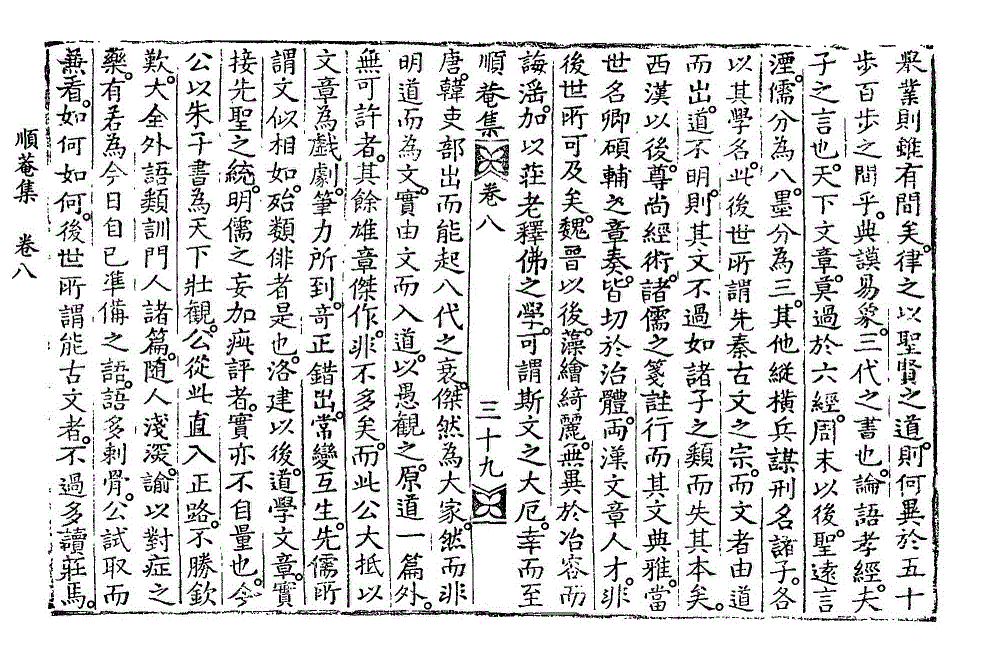 举业则虽有间矣。律之以圣贤之道。则何异于五十步百步之间乎。典谟易象。三代之书也。论语孝经。夫子之言也。天下文章。莫过于六经。周末以后。圣远言湮。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其他纵横兵谋刑名诸子。各以其学名。此后世所谓先秦古文之宗。而文者由道而出。道不明。则其文不过如诸子之类而失其本矣。西汉以后。尊尚经术。诸儒之笺注行而其文典雅。当世名卿硕辅之章奏。皆切于治体。两汉文章人才。非后世所可及矣。魏晋以后。藻绘绮丽。无异于冶容而诲淫。加以庄老释佛之学。可谓斯文之大厄。幸而至唐。韩吏部出而能起八代之衰。杰然为大家。然而非明道而为文。实由文而入道。以愚观之。原道一篇外。无可许者。其馀雄章杰作。非不多矣。而此公大抵以文章为戏剧。笔力所到。奇正错出。常变互生。先儒所谓文似相如。殆类俳者是也。洛建以后。道学文章。实接先圣之统。明儒之妄加疵评者。实亦不自量也。今公以朱子书为天下壮观。公从此直入正路。不胜钦叹。大全外语类训门人诸篇。随人浅深。谕以对症之药。有若为今日自己准备之语。语多刺骨。公试取而兼看。如何如何。后世所谓能古文者。不过多读庄马。
举业则虽有间矣。律之以圣贤之道。则何异于五十步百步之间乎。典谟易象。三代之书也。论语孝经。夫子之言也。天下文章。莫过于六经。周末以后。圣远言湮。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其他纵横兵谋刑名诸子。各以其学名。此后世所谓先秦古文之宗。而文者由道而出。道不明。则其文不过如诸子之类而失其本矣。西汉以后。尊尚经术。诸儒之笺注行而其文典雅。当世名卿硕辅之章奏。皆切于治体。两汉文章人才。非后世所可及矣。魏晋以后。藻绘绮丽。无异于冶容而诲淫。加以庄老释佛之学。可谓斯文之大厄。幸而至唐。韩吏部出而能起八代之衰。杰然为大家。然而非明道而为文。实由文而入道。以愚观之。原道一篇外。无可许者。其馀雄章杰作。非不多矣。而此公大抵以文章为戏剧。笔力所到。奇正错出。常变互生。先儒所谓文似相如。殆类俳者是也。洛建以后。道学文章。实接先圣之统。明儒之妄加疵评者。实亦不自量也。今公以朱子书为天下壮观。公从此直入正路。不胜钦叹。大全外语类训门人诸篇。随人浅深。谕以对症之药。有若为今日自己准备之语。语多刺骨。公试取而兼看。如何如何。后世所谓能古文者。不过多读庄马。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5L 页
 助其辞华。旁猎先秦古文之艰棘句语。务为深僻之辞。饰其浅短之见。使人不能读去。谓之古文。古文岂如是哉。又有以是为病者。务顺其文。支离其语。汗漫其辞。陈谈陋说。街言巷语。杂采成篇。谓之曰古人辞达之义。辞达之义。岂如是哉。六经之文。果是辞达。而其深也。贯天人通物理而无所隐。其易也。驰风帆走冰匏而无所碍。言正理顺。曲畅旁通。如是而后。可谓辞达。此亦岂易言哉。以愚观之。惟朱子可以当之。后来儒者之文。大抵误认辞达之义而失其本矣。今公于力学古文之馀。以朱文为第一义。是实斯文之幸而可为后进之津筏矣。汉北人人皆以为我知。故不敢发此等语。盛问之下。不敢自外。语多狂率。是悚是悚。书末所谕乍掇丹铅。专意颐养之教。深感深感。虽自知其病。而恒多未了之业。浪费神精。居常自悼。向者来游一少年。专意于务博。临别口赠一诗曰。学问虽在博。要以约为守。终日数人钱。一文非己有。沿门持钵客。竟未饱其口。游骑戒太远。无成至白首。寄语后来者。慎勿效此叟。公见之。亦必一笑矣。今世吾道殆将绝矣。此中染于异学。非我只手可障。惟冀山南诸友益懋大业。以幸吾道。死生之望。
助其辞华。旁猎先秦古文之艰棘句语。务为深僻之辞。饰其浅短之见。使人不能读去。谓之古文。古文岂如是哉。又有以是为病者。务顺其文。支离其语。汗漫其辞。陈谈陋说。街言巷语。杂采成篇。谓之曰古人辞达之义。辞达之义。岂如是哉。六经之文。果是辞达。而其深也。贯天人通物理而无所隐。其易也。驰风帆走冰匏而无所碍。言正理顺。曲畅旁通。如是而后。可谓辞达。此亦岂易言哉。以愚观之。惟朱子可以当之。后来儒者之文。大抵误认辞达之义而失其本矣。今公于力学古文之馀。以朱文为第一义。是实斯文之幸而可为后进之津筏矣。汉北人人皆以为我知。故不敢发此等语。盛问之下。不敢自外。语多狂率。是悚是悚。书末所谕乍掇丹铅。专意颐养之教。深感深感。虽自知其病。而恒多未了之业。浪费神精。居常自悼。向者来游一少年。专意于务博。临别口赠一诗曰。学问虽在博。要以约为守。终日数人钱。一文非己有。沿门持钵客。竟未饱其口。游骑戒太远。无成至白首。寄语后来者。慎勿效此叟。公见之。亦必一笑矣。今世吾道殆将绝矣。此中染于异学。非我只手可障。惟冀山南诸友益懋大业。以幸吾道。死生之望。与郑都事士仰(宗鲁)书(己酉)
夙仰声华。恒有愿言之怀。顷蒙临顾。实协所愿。慰感多矣。第逢别悤悤。不得稳承绪论。怅惘馀怀。不胜形喻。比来寒威渐紧。不审侍馀进德有常。仰溸仰溸。鼎福癃废馀喘。年数压重。鬼事日迫。百疾交侵。惟待大限之将至耳。自念少时些少志气。中以病废。惟冀少友中有担负之望者。向接芝宇温温近道之姿。嘐嘐曰古之意。自难掩焉。心乎爱矣。何日忘之。南宗伯亦能弃举业。专意此事。于尊可谓德必有邻矣。惟乞益懋大业。以慰斯文之望。不宣。
与柳敬之(警)书(乙未)
向来山寺之业。想有隽永。恨不得奉叩绪论也。少日读书。略有知解。虽自为喜。而多是虚影。不见实际。中间病废。因以滚到此下舂世界。而白纷无成。近来渐觉意味深长。圣贤言语一句非虚。有时感激。咎悔山积。而鼎器已亏。城郭不完。将无所施其功矣。只自悼叹。为学之要。不过务实二字。公向读大学。试以大学首句言之。所谓明德。是得之于天。人皆有之。若任其昏蔽。不下明之之工。则循人欲而坠天命。其违禽兽不远矣。是以必欲其明其明德。以保守我惟天所降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6L 页
 之衷而存养之。上明字。即致知之工也。下明字。即所得乎天之明命而为我德之本体者也。徒下明之之工而忽于存省。则为偏枯之学。而明德之本体。不能自保矣。此知行之所以相须而不可离者也。故读此句。不徒一番吟咏而已。必以实心求之。实心行之。诸书读法皆如此。然后庶几为我之有而真可谓之实学也。颜子以亚圣之姿。初闻圣师之教。不过曰克己复礼为仁。其下申之以非礼勿视听言动四者之目。视听言动。圣凡之所同也。非有高远玄妙难知难行之事矣。知其为礼属知。勿字属行。颜子自闻是教。实心奉承。凡遇事物。必审其礼与非礼。知其为非礼则勿之行焉。造次颠沛。不少忽焉。积习之久。人欲自绝。天理浑然。至于三月而不违仁。乃喟然叹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及其问为邦。又告之以四代之礼乐。非若诸子问政。各举一事而指教之。其为圣师之所许。如是之大。则颜子所造之地位。亦可想矣。以颜子之圣。而其初用功。止于四勿。则圣门教人之法。后学承受之节。皆当以此始矣。后世言词胜而实业亡。口谈天人性命之说。而却忽于下学上达之义。此百世所以无真儒也。愚尝以为凡为学。当观
之衷而存养之。上明字。即致知之工也。下明字。即所得乎天之明命而为我德之本体者也。徒下明之之工而忽于存省。则为偏枯之学。而明德之本体。不能自保矣。此知行之所以相须而不可离者也。故读此句。不徒一番吟咏而已。必以实心求之。实心行之。诸书读法皆如此。然后庶几为我之有而真可谓之实学也。颜子以亚圣之姿。初闻圣师之教。不过曰克己复礼为仁。其下申之以非礼勿视听言动四者之目。视听言动。圣凡之所同也。非有高远玄妙难知难行之事矣。知其为礼属知。勿字属行。颜子自闻是教。实心奉承。凡遇事物。必审其礼与非礼。知其为非礼则勿之行焉。造次颠沛。不少忽焉。积习之久。人欲自绝。天理浑然。至于三月而不违仁。乃喟然叹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及其问为邦。又告之以四代之礼乐。非若诸子问政。各举一事而指教之。其为圣师之所许。如是之大。则颜子所造之地位。亦可想矣。以颜子之圣。而其初用功。止于四勿。则圣门教人之法。后学承受之节。皆当以此始矣。后世言词胜而实业亡。口谈天人性命之说。而却忽于下学上达之义。此百世所以无真儒也。愚尝以为凡为学。当观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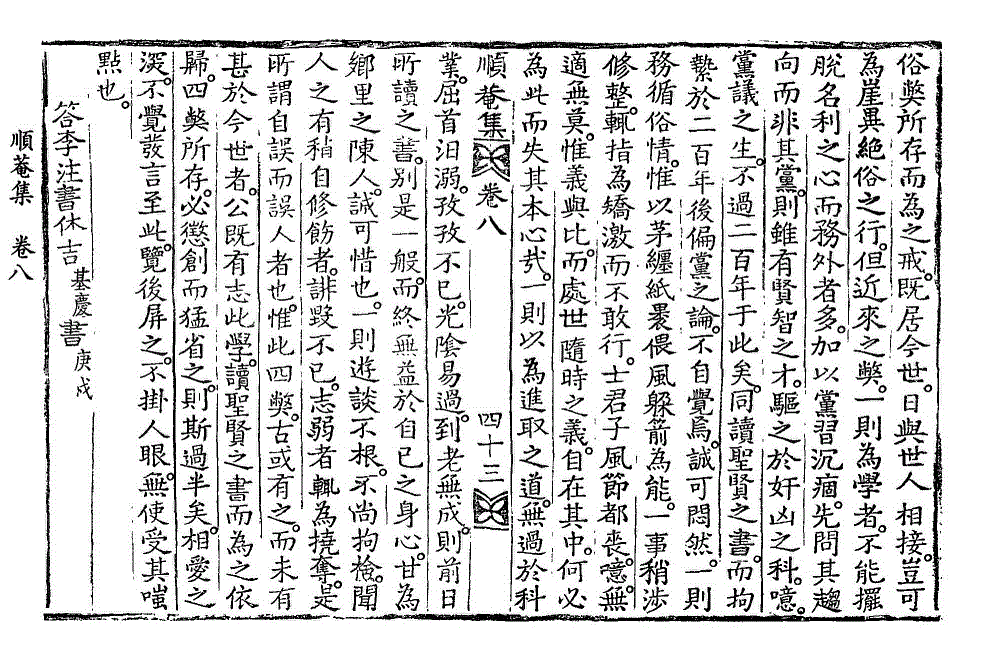 俗弊所存而为之戒。既居今世。日与世人相接。岂可为崖异绝俗之行。但近来之弊。一则为学者。不能摆脱名利之心而务外者多。加以党习沉痼。先问其趋向而非其党。则虽有贤智之才。驱之于奸凶之科。噫。党议之生。不过二百年于此矣。同读圣贤之书。而拘絷于二百年后偏党之论。不自觉焉。诚可闷然。一则务循俗情。惟以茅缠纸裹偎风躲箭为能。一事稍涉修整。辄指为矫激而不敢行。士君子风节都丧。噫。无适无莫。惟义与比。而处世随时之义。自在其中。何必为此而失其本心哉。一则以为进取之道。无过于科业。屈首汨溺。孜孜不已。光阴易过。到老无成。则前日所读之书。别是一般。而终无益于自己之身心。甘为乡里之陈人。诚可惜也。一则游谈不根。不尚拘检。闻人之有稍自修饬者。诽毁不已。志弱者辄为挠夺。是所谓自误而误人者也。惟此四弊。古或有之。而未有甚于今世者。公既有志此学。读圣贤之书而为之依归。四弊所存。必惩创而猛省之。则斯过半矣。相爱之深。不觉发言至此。览后屏之。不挂人眼。无使受其嗤点也。
俗弊所存而为之戒。既居今世。日与世人相接。岂可为崖异绝俗之行。但近来之弊。一则为学者。不能摆脱名利之心而务外者多。加以党习沉痼。先问其趋向而非其党。则虽有贤智之才。驱之于奸凶之科。噫。党议之生。不过二百年于此矣。同读圣贤之书。而拘絷于二百年后偏党之论。不自觉焉。诚可闷然。一则务循俗情。惟以茅缠纸裹偎风躲箭为能。一事稍涉修整。辄指为矫激而不敢行。士君子风节都丧。噫。无适无莫。惟义与比。而处世随时之义。自在其中。何必为此而失其本心哉。一则以为进取之道。无过于科业。屈首汨溺。孜孜不已。光阴易过。到老无成。则前日所读之书。别是一般。而终无益于自己之身心。甘为乡里之陈人。诚可惜也。一则游谈不根。不尚拘检。闻人之有稍自修饬者。诽毁不已。志弱者辄为挠夺。是所谓自误而误人者也。惟此四弊。古或有之。而未有甚于今世者。公既有志此学。读圣贤之书而为之依归。四弊所存。必惩创而猛省之。则斯过半矣。相爱之深。不觉发言至此。览后屏之。不挂人眼。无使受其嗤点也。答李注书休吉(基庆)书(庚戌)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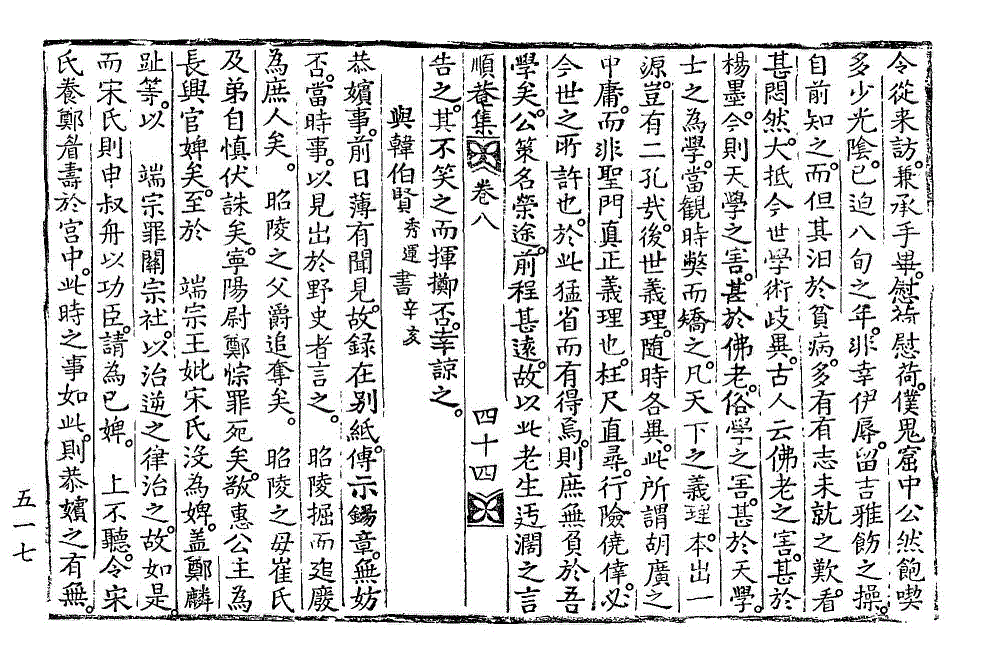 令从来访。兼承手毕。慰荷慰荷。仆鬼窟中公然饱吃多少光阴。已迫八旬之年。非幸伊辱。留吉雅饬之操。自前知之。而但其汨于贫病。多有有志未就之叹。看甚闷然。大抵今世学术歧异。古人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今则天学之害。甚于佛老。俗学之害。甚于天学。士之为学。当观时弊而矫之。凡天下之义理。本出一源。岂有二孔哉。后世义理。随时各异。此所谓胡广之中庸。而非圣门真正义理也。枉尺直寻。行险侥倖。必今世之所许也。于此猛省而有得焉。则庶无负于吾学矣。公策名荣途。前程甚远。故以此老生迂阔之言告之。其不笑之而挥掷否。幸谅之。
令从来访。兼承手毕。慰荷慰荷。仆鬼窟中公然饱吃多少光阴。已迫八旬之年。非幸伊辱。留吉雅饬之操。自前知之。而但其汨于贫病。多有有志未就之叹。看甚闷然。大抵今世学术歧异。古人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今则天学之害。甚于佛老。俗学之害。甚于天学。士之为学。当观时弊而矫之。凡天下之义理。本出一源。岂有二孔哉。后世义理。随时各异。此所谓胡广之中庸。而非圣门真正义理也。枉尺直寻。行险侥倖。必今世之所许也。于此猛省而有得焉。则庶无负于吾学矣。公策名荣途。前程甚远。故以此老生迂阔之言告之。其不笑之而挥掷否。幸谅之。与韩伯贤(秀运)书(辛亥)
恭嫔事。前日薄有闻见。故录在别纸。传示铴章。无妨否。当时事。以见出于野史者言之。 昭陵掘而追废为庶人矣。 昭陵之父爵追夺矣。 昭陵之母崔氏及弟自慎伏诛矣。宁阳尉郑悰罪死矣。敬惠公主为长兴官婢矣。至于 端宗王妣宋氏没为婢。盖郑麟趾等。以 端宗罪关宗社。以治逆之律治之。故如是。而宋氏则申叔舟以功臣。请为己婢。 上不听。令宋氏养郑眉寿于宫中。此时之事如此。则恭嫔之有无。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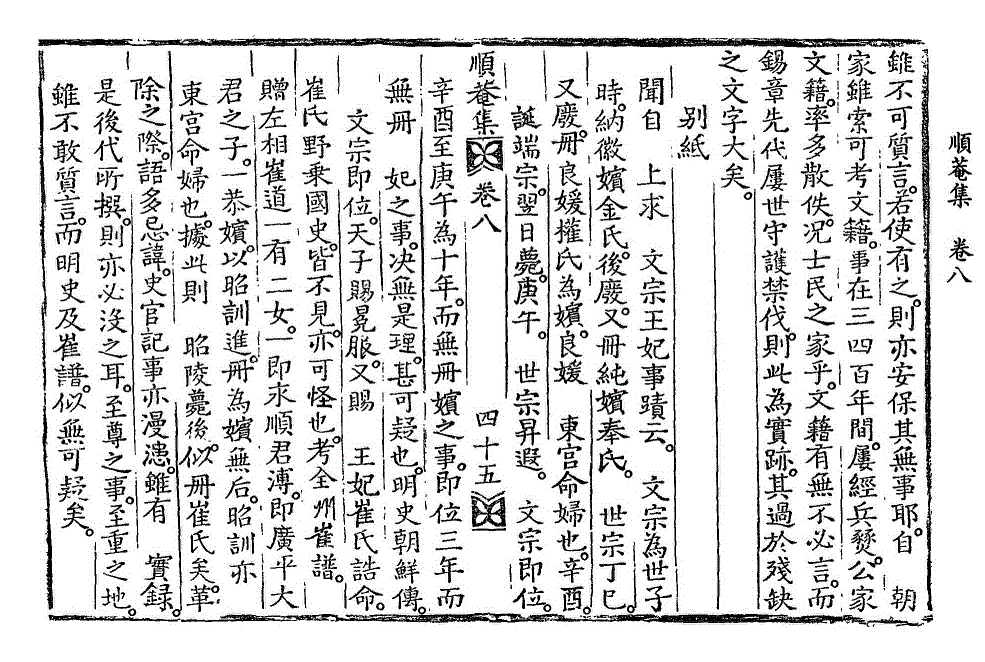 虽不可质言。若使有之。则亦安保其无事耶。自 朝家虽索可考文籍。事在三四百年间。屡经兵燹。公家文籍。率多散佚。况士民之家乎。文籍有无不必言。而锡章先代屡世守护禁伐。则此为实迹。其过于残缺之文字大矣。
虽不可质言。若使有之。则亦安保其无事耶。自 朝家虽索可考文籍。事在三四百年间。屡经兵燹。公家文籍。率多散佚。况士民之家乎。文籍有无不必言。而锡章先代屡世守护禁伐。则此为实迹。其过于残缺之文字大矣。别纸
闻自 上求 文宗王妃事迹云。 文宗为世子时。纳徽嫔金氏。后废。又册纯嫔奉氏。 世宗丁巳。又废。册良媛权氏为嫔。良媛 东宫命妇也。辛酉。 诞端宗。翌日薨。庚午。 世宗升遐。 文宗即位。辛酉至庚午为十年。而无册嫔之事。即位三年而无册 妃之事。决无是理。甚可疑也。明史朝鲜传。 文宗即位。天子赐冕服。又赐 王妃崔氏诰命。崔氏野乘国史。皆不见。亦可怪也。考全州崔谱。 赠左相崔道一有二女。一即永顺君溥。即广平大君之子。一恭嫔。以昭训进。册为嫔无后。昭训亦 东宫命妇也。据此则 昭陵薨后。似册崔氏矣。革除之际。语多忌讳。史官记事亦漫漶。虽有 实录。是后代所撰。则亦必没之耳。至尊之事。至重之地。虽不敢质言。而明史及崔谱。似无可疑矣。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8L 页
 又
又示谕恭嫔事。愚见十分无疑矣。考崔谱。连三代国婚。崔士康之女二。适諴宁君䄄,锦城大君瑜。士康之子承宁女适临瀛大君璆。承宁之子道一二女。一适永顺君溥。广平大君玙之子也。一即恭嫔无后。以昭训进为嫔。昭训 东宫命妇也。此时 东宫册嫔。非 文宗而何。且道一官礼储仓丞。殁后 赠左相。国典。 王妣考 赠领相。 世子嫔考 赠左相。 世孙嫔考 赠右相。左相之 赠。非 世子嫔考而何。 端宗之姊敬惠公主下嫁宁阳尉郑悰。墓在高阳。恭嫔之祔葬于公主墓侧。似非异事。况崔家流传之语。以恭嫔无后。故自 上定墓于公主墓侧。奉祀则使崔氏本家举行。定墓直香火禁伐云。则其说信矣。向来虽有三 朝实录考出之事。 实录之疏漏亦多。况革除之时。事多忌讳。史官之不能直书者必多。又况 实录之撰。出于后代。亦安知非史官之随意刊削而然耶。其时法令甚严。私家野史。亦不敢记录。理势固然。但恭嫔二字。足为的实之断案矣。明史朝鲜传。列朝 王妣诰命。皆书姓氏。不独崔氏然也。自 上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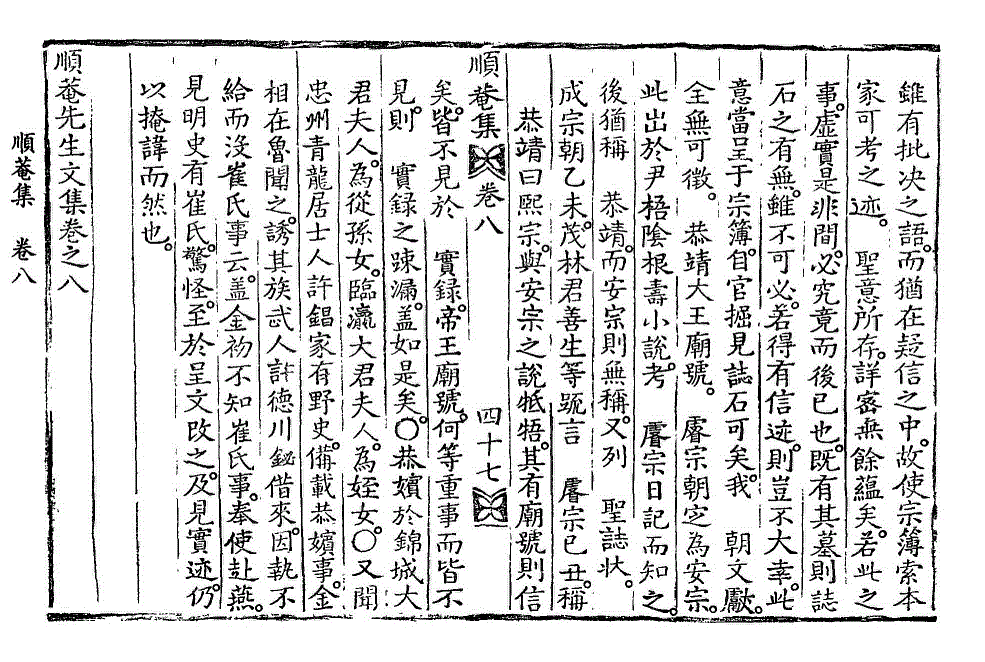 虽有批决之语。而犹在疑信之中。故使宗簿索本家可考之迹。 圣意所存。详密无馀蕴矣。若此之事。虚实是非间。必究竟而后已也。既有其墓则志石之有无。虽不可必。若得有信迹。则岂不大幸。此意当呈于宗簿。自官掘见志石可矣。我 朝文献。全无可徵。 恭靖大王庙号。 睿宗朝定为安宗。此出于尹梧阴根寿小说。考 睿宗日记而知之。后犹称 恭靖。而安宗则无称。又列 圣志状。 成宗朝乙未。茂林君善生等疏言 睿宗己丑。称 恭靖曰熙宗。与安宗之说牴牾。其有庙号则信矣。皆不见于 实录。帝王庙号。何等重事而皆不见。则 实录之疏漏。盖如是矣。○恭嫔于锦城大君夫人。为从孙女。临瀛大君夫人。为侄女。○又闻忠州青龙居士人许锠家有野史。备载恭嫔事。金相在鲁闻之。诱其族武人许德川铋借来。因执不给而没崔氏事云。盖金初不知崔氏事。奉使赴燕。见明史有崔氏。惊怪。至于呈文改之。及见实迹。仍以掩讳而然也。
虽有批决之语。而犹在疑信之中。故使宗簿索本家可考之迹。 圣意所存。详密无馀蕴矣。若此之事。虚实是非间。必究竟而后已也。既有其墓则志石之有无。虽不可必。若得有信迹。则岂不大幸。此意当呈于宗簿。自官掘见志石可矣。我 朝文献。全无可徵。 恭靖大王庙号。 睿宗朝定为安宗。此出于尹梧阴根寿小说。考 睿宗日记而知之。后犹称 恭靖。而安宗则无称。又列 圣志状。 成宗朝乙未。茂林君善生等疏言 睿宗己丑。称 恭靖曰熙宗。与安宗之说牴牾。其有庙号则信矣。皆不见于 实录。帝王庙号。何等重事而皆不见。则 实录之疏漏。盖如是矣。○恭嫔于锦城大君夫人。为从孙女。临瀛大君夫人。为侄女。○又闻忠州青龙居士人许锠家有野史。备载恭嫔事。金相在鲁闻之。诱其族武人许德川铋借来。因执不给而没崔氏事云。盖金初不知崔氏事。奉使赴燕。见明史有崔氏。惊怪。至于呈文改之。及见实迹。仍以掩讳而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