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杂著(经义)
杂著(经义)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28H 页
 大学(辛丑)
大学(辛丑)经一章
心也性也。一也。在所指如何耳。程子曰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乾即性也。帝与神则心也。其在人者亦然。是故言性则心自举。言心则性在中。如中庸天命之性是说性。而下即言喜怒哀乐之发未发则性亦心也。大学致知是说心。而下即承之以致知在格物则心亦性也。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语意浑然。无少罅缝。而心性真面目。卓然现前。可谓深切著明矣。于此看得分明则大学第一句明德二字。无他。只是指此物以示人。先儒谓合心性者固得矣。然才下合字。便觉钝滞了。学者以意会之可矣。程子所谓形体之天在人。则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张子所谓湛一气之本者也。心其灵而性其德也。无此气则心与性之名。亦无自以立矣。
朱子元亨利贞说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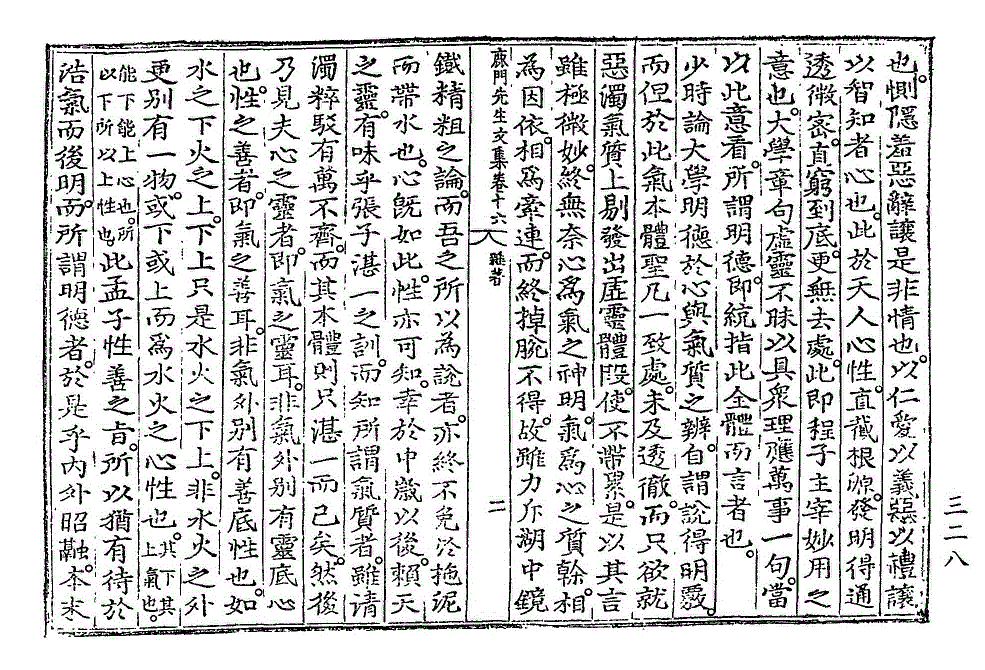 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此于天人心性。直截根源。发明得通透微密。直穷到底。更无去处。此即程子主宰妙用之意也。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一句。当以此意看。所谓明德。即统指此全体而言者也。
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此于天人心性。直截根源。发明得通透微密。直穷到底。更无去处。此即程子主宰妙用之意也。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一句。当以此意看。所谓明德。即统指此全体而言者也。少时论大学明德于心与气质之辨。自谓说得明覈。而但于此气本体圣凡一致处。未及透彻。而只欲就恶浊气质上剔发出虚灵体段。使不带累。是以其言虽极微妙。终无奈心为气之神明。气为心之质干。相为因依。相为牵连。而终掉脱不得。故虽力斥湖中镜铁精粗之论。而吾之所以为说者。亦终不免于拖泥而带水也。心既如此。性亦可知。幸于中岁以后。赖天之灵。有味乎张子湛一之训。而知所谓气质者。虽清浊粹驳有万不齐。而其本体则只湛一而已矣。然后乃见夫心之灵者。即气之灵耳。非气外别有灵底心也。性之善者。即气之善耳。非气外别有善底性也。如水之下火之上。下上只是水火之下上。非水火之外更别有一物。或下或上而为水火之心性也。(其下其上气也。能下能上心也。所以下所以上性也。)此孟子性善之旨。所以犹有待于浩气而后明。而所谓明德者。于是乎内外昭融。本末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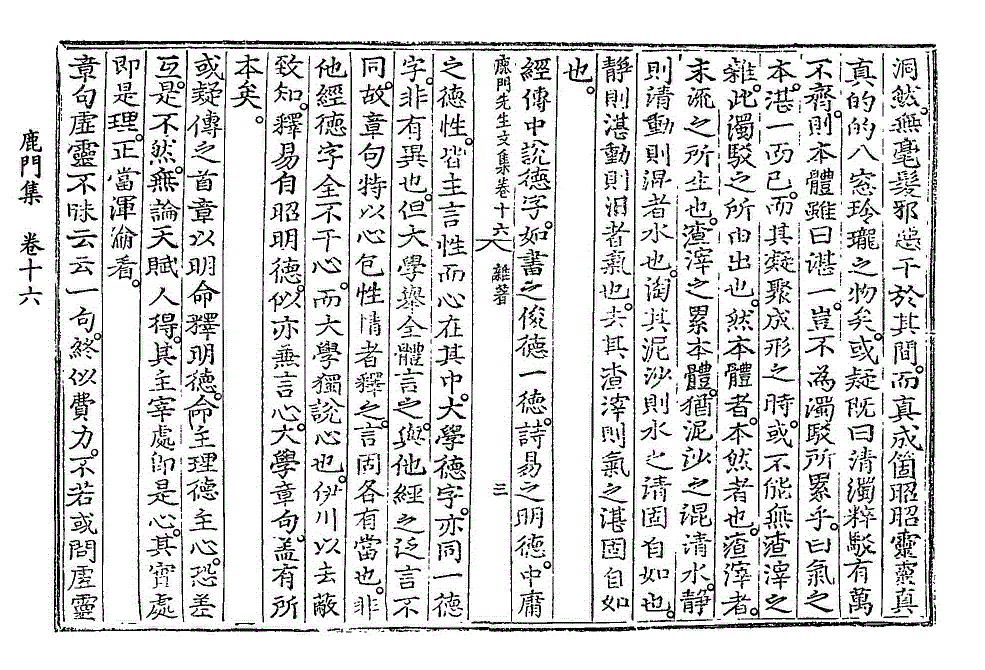 洞然。无毫发邪恶干于其间。而真成个昭昭灵灵真真的的八窗玲珑之物矣。或疑既曰清浊粹驳有万不齐。则本体虽曰湛一。岂不为浊驳所累乎。曰气之本。湛一而已。而其凝聚成形之时。或不能无渣滓之杂。此浊驳之所由出也。然本体者。本然者也。渣滓者。末流之所生也。渣滓之累本体。犹泥沙之混清水。静则清动则混者水也。淘其泥沙则水之清固自如也。静则湛动则汨者气也。去其渣滓则气之湛固自如也。
洞然。无毫发邪恶干于其间。而真成个昭昭灵灵真真的的八窗玲珑之物矣。或疑既曰清浊粹驳有万不齐。则本体虽曰湛一。岂不为浊驳所累乎。曰气之本。湛一而已。而其凝聚成形之时。或不能无渣滓之杂。此浊驳之所由出也。然本体者。本然者也。渣滓者。末流之所生也。渣滓之累本体。犹泥沙之混清水。静则清动则混者水也。淘其泥沙则水之清固自如也。静则湛动则汨者气也。去其渣滓则气之湛固自如也。经传中说德字。如书之俊德一德。诗易之明德。中庸之德性。皆主言性而心在其中。大学德字。亦同一德字。非有异也。但大学举全体言之。与他经之泛言不同。故章句特以心包性情者释之。言固各有当也。非他经德字全不干心。而大学独说心也。伊川以去蔽致知。释易自昭明德。似亦兼言心。大学章句。盖有所本矣。
或疑传之首章以明命释明德。命主理德主心。恐差互。是不然。无论天赋人得。其主宰处即是心。其实处即是理。正当浑沦看。
章句虚灵不昧云云一句。终似费力。不若或问虚灵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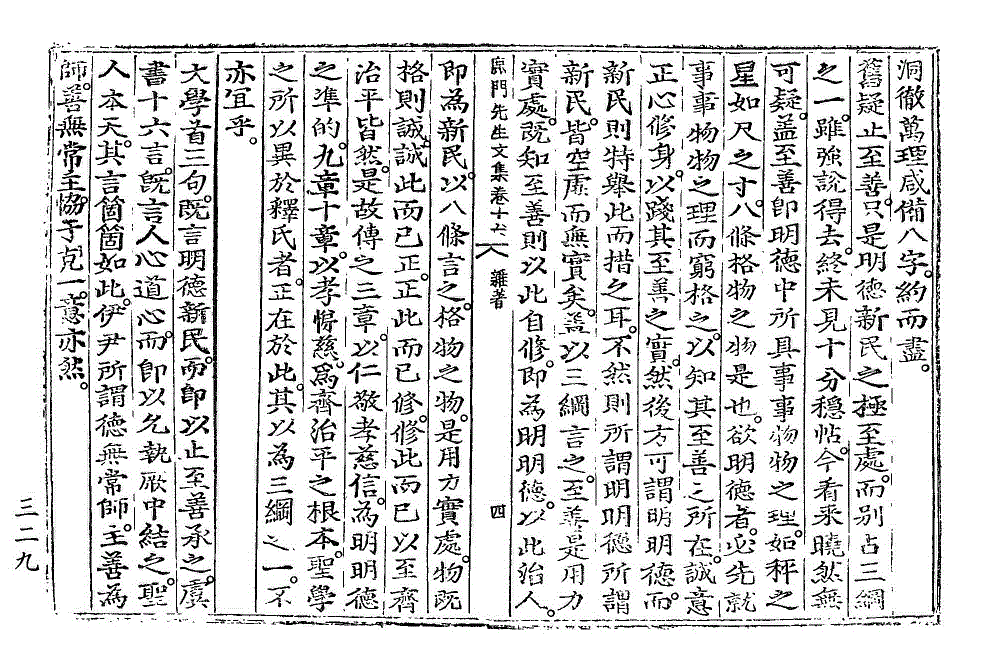 洞彻万理咸备八字。约而尽。
洞彻万理咸备八字。约而尽。旧疑止至善。只是明德新民之极至处。而别占三纲之一。虽强说得去。终未见十分稳帖。今看来晓然无可疑。盖至善即明德中所具事事物物之理。如秤之星如尺之寸。八条格物之物是也。欲明德者。必先就事事物物之理而穷格之。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诚意正心修身。以践其至善之实。然后方可谓明明德。而新民则特举此而措之耳。不然则所谓明明德所谓新民。皆空虚而无实矣。盖以三纲言之。至善是用力实处。既知至善则以此自修。即为明明德。以此治人。即为新民。以八条言之。格物之物。是用力实处。物既格则诚。诚此而己正。正此而己修。修此而己以至齐治平皆然。是故传之三章。以仁敬孝慈信。为明明德之准的。九章十章。以孝悌慈。为齐治平之根本。圣学之所以异于释氏者。正在于此。其以为三纲之一。不亦宜乎。
大学首三句。既言明德新民。而即以止至善承之。虞书十六言。既言人心道心。而即以允执厥中结之。圣人本天。其言个个如此。伊尹所谓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意亦然。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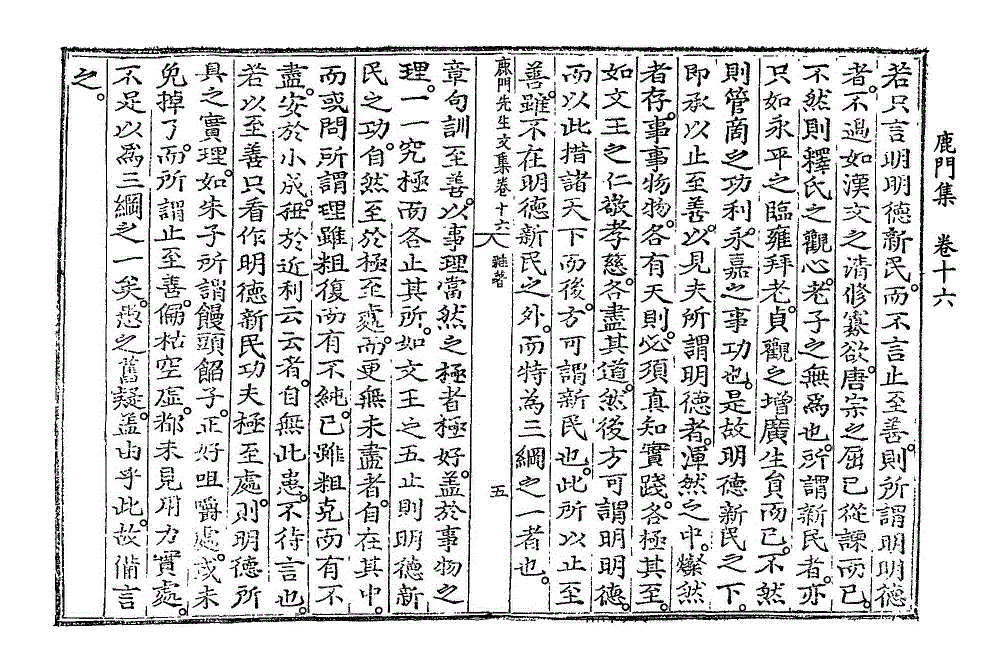 若只言明明德,新民。而不言止至善。则所谓明明德者。不过如汉文之清修寡欲。唐宗之屈己从谏而已。不然则释氏之观心。老子之无为也。所谓新民者。亦只如永平之临雍拜老。贞观之增广生员而已。不然则管商之功利。永嘉之事功也。是故明德新民之下。即承以止至善。以见夫所谓明德者。浑然之中。灿然者存。事事物物。各有天则。必须真知实践。各极其至。如文王之仁敬孝慈。各尽其道。然后方可谓明明德。而以此措诸天下而后。方可谓新民也。此所以止至善。虽不在明德,新民之外。而特为三纲之一者也。
若只言明明德,新民。而不言止至善。则所谓明明德者。不过如汉文之清修寡欲。唐宗之屈己从谏而已。不然则释氏之观心。老子之无为也。所谓新民者。亦只如永平之临雍拜老。贞观之增广生员而已。不然则管商之功利。永嘉之事功也。是故明德新民之下。即承以止至善。以见夫所谓明德者。浑然之中。灿然者存。事事物物。各有天则。必须真知实践。各极其至。如文王之仁敬孝慈。各尽其道。然后方可谓明明德。而以此措诸天下而后。方可谓新民也。此所以止至善。虽不在明德,新民之外。而特为三纲之一者也。章句训至善。以事理当然之极者极好。盖于事物之理。一一究极而各止其所。如文王之五止则明德新民之功。自然至于极至处。而更无未尽者。自在其中。而或问所谓理虽粗复而有不纯。己虽粗克而有不尽。安于小成。狃于近利云云者。自无此患。不待言也。若以至善只看作明德新民功夫极至处。则明德所具之实理。如朱子所谓馒头馅子。正好咀嚼处。或未免掉了。而所谓止至善。偏枯空虚。都未见用力实处。不足以为三纲之一矣。愚之旧疑。盖由乎此。故备言之。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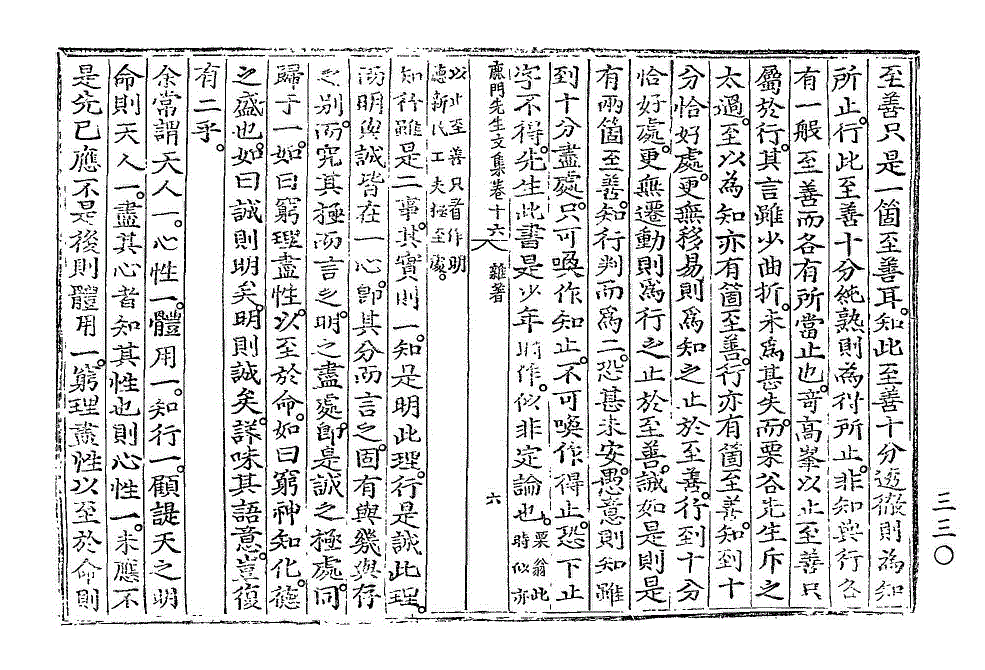 至善只是一个至善耳。知此至善十分透彻则为知所止。行此至善十分纯熟则为得所止。非知与行各有一般至善而各有所当止也。奇高峰以止至善只属于行。其言虽少曲折。未为甚失。而栗谷先生斥之太过。至以为知亦有个至善。行亦有个至善。知到十分恰好处。更无移易则为知之止于至善。行到十分恰好处。更无迁动则为行之止于至善。诚如是则是有两个至善。知行判而为二。恐甚未安。愚意则知虽到十分尽处。只可唤作知止。不可唤作得止。恐下止字不得。先生此书是少年时作。似非定论也。(栗翁此时似亦以止至善只看作明德,新民工夫极至处。)
至善只是一个至善耳。知此至善十分透彻则为知所止。行此至善十分纯熟则为得所止。非知与行各有一般至善而各有所当止也。奇高峰以止至善只属于行。其言虽少曲折。未为甚失。而栗谷先生斥之太过。至以为知亦有个至善。行亦有个至善。知到十分恰好处。更无移易则为知之止于至善。行到十分恰好处。更无迁动则为行之止于至善。诚如是则是有两个至善。知行判而为二。恐甚未安。愚意则知虽到十分尽处。只可唤作知止。不可唤作得止。恐下止字不得。先生此书是少年时作。似非定论也。(栗翁此时似亦以止至善只看作明德,新民工夫极至处。)知行虽是二事。其实则一。知是明此理。行是诚此理。而明与诚皆在一心。即其分而言之。固有与几与存之别。而究其极而言之。明之尽处。即是诚之极处。同归于一。如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详味其语意。岂复有二乎。
余常谓天人一。心性一。体用一。知行一。顾諟天之明命则天人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心性一。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则体用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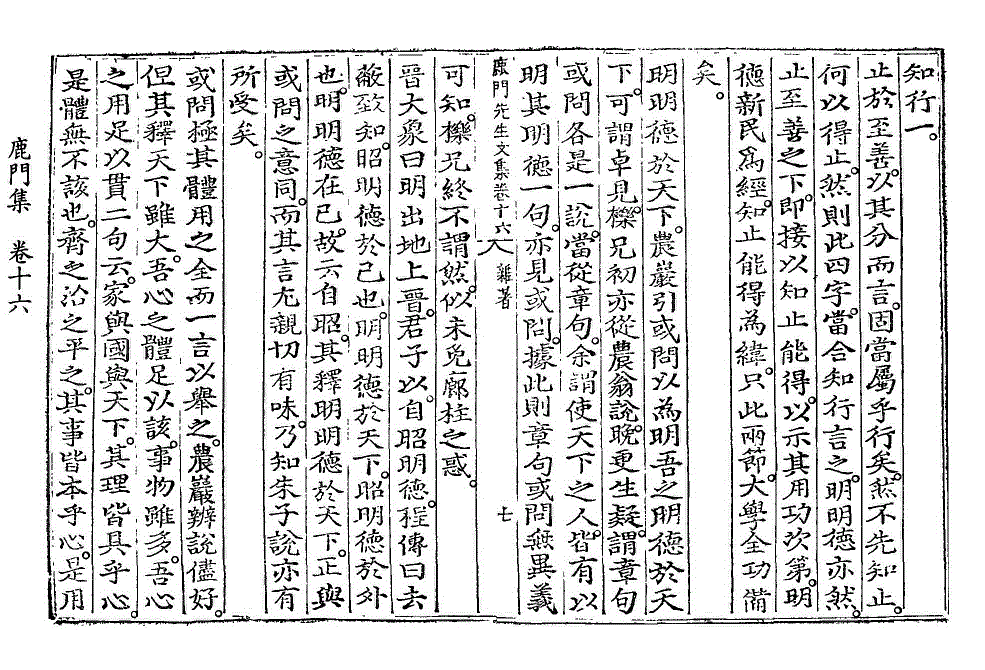 知行一。
知行一。止于至善。以其分而言。固当属乎行矣。然不先知止。何以得止。然则此四字。当合知行言之。明明德亦然。止至善之下。即接以知止能得。以示其用功次第。明德新民为经。知止能得为纬。只此两节。大学全功备矣。
明明德于天下。农岩引或问以为明吾之明德于天下。可谓卓见。栎兄初亦从农翁说。晚更生疑。谓章句或问各是一说。当从章句。余谓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一句。亦见或问。据此则章句或问无异义可知。栎兄终不谓然。似未免廊柱之惑。
晋大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程传曰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其释明明德于天下。正与或问之意同。而其言尤亲切有味。乃知朱子说亦有所受矣。
或问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农岩辨说尽好。但其释天下虽大。吾心之体足以该。事物虽多。吾心之用足以贯二句云。家与国与天下。其理皆具乎心。是体无不该也。齐之治之平之。其事皆本乎心。是用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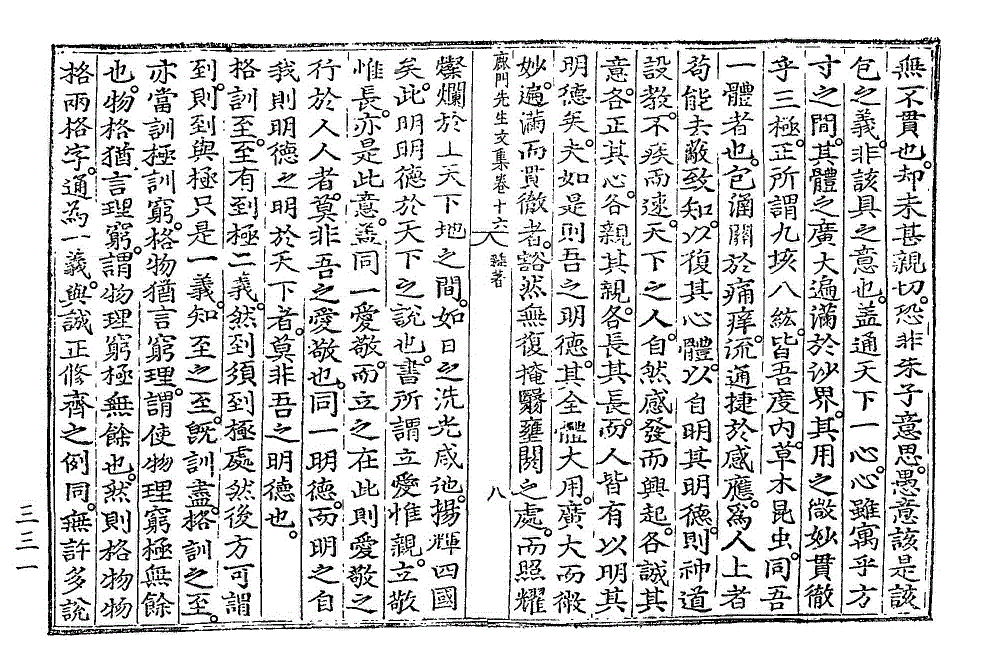 无不贯也。却未甚亲切。恐非朱子意思。愚意该是该包之义。非该具之意也。盖通天下一心。心虽寓乎方寸之间。其体之广大遍满于沙界。其用之微妙贯彻乎三极。正所谓九垓八纮。皆吾度内。草木昆虫。同吾一体者也。包涵关于痛痒。流通捷于感应。为人上者苟能去蔽致知。以复其心体。以自明其明德。则神道设教。不疾而速。天下之人。自然感发而兴起。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夫如是则吾之明德。其全体大用。广大而微妙。遍满而贯彻者。豁然无复掩翳壅阏之处。而照耀灿烂于上天下地之间。如日之洗光咸池。扬辉四国矣。此明明德于天下之说也。书所谓立爱惟亲。立敬惟长。亦是此意。盖同一爱敬。而立之在此则爱敬之行于人人者。莫非吾之爱敬也。同一明德。而明之自我则明德之明于天下者。莫非吾之明德也。
无不贯也。却未甚亲切。恐非朱子意思。愚意该是该包之义。非该具之意也。盖通天下一心。心虽寓乎方寸之间。其体之广大遍满于沙界。其用之微妙贯彻乎三极。正所谓九垓八纮。皆吾度内。草木昆虫。同吾一体者也。包涵关于痛痒。流通捷于感应。为人上者苟能去蔽致知。以复其心体。以自明其明德。则神道设教。不疾而速。天下之人。自然感发而兴起。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夫如是则吾之明德。其全体大用。广大而微妙。遍满而贯彻者。豁然无复掩翳壅阏之处。而照耀灿烂于上天下地之间。如日之洗光咸池。扬辉四国矣。此明明德于天下之说也。书所谓立爱惟亲。立敬惟长。亦是此意。盖同一爱敬。而立之在此则爱敬之行于人人者。莫非吾之爱敬也。同一明德。而明之自我则明德之明于天下者。莫非吾之明德也。格训至。至有到极二义。然到须到极处然后方可谓到。则到与极只是一义。知至之至。既训尽。格训之至。亦当训极训穷。格物犹言穷理。谓使物理穷极无馀也。物格犹言理穷。谓物理穷极无馀也。然则格物物格两格字。通为一义。与诚正修齐之例同。无许多说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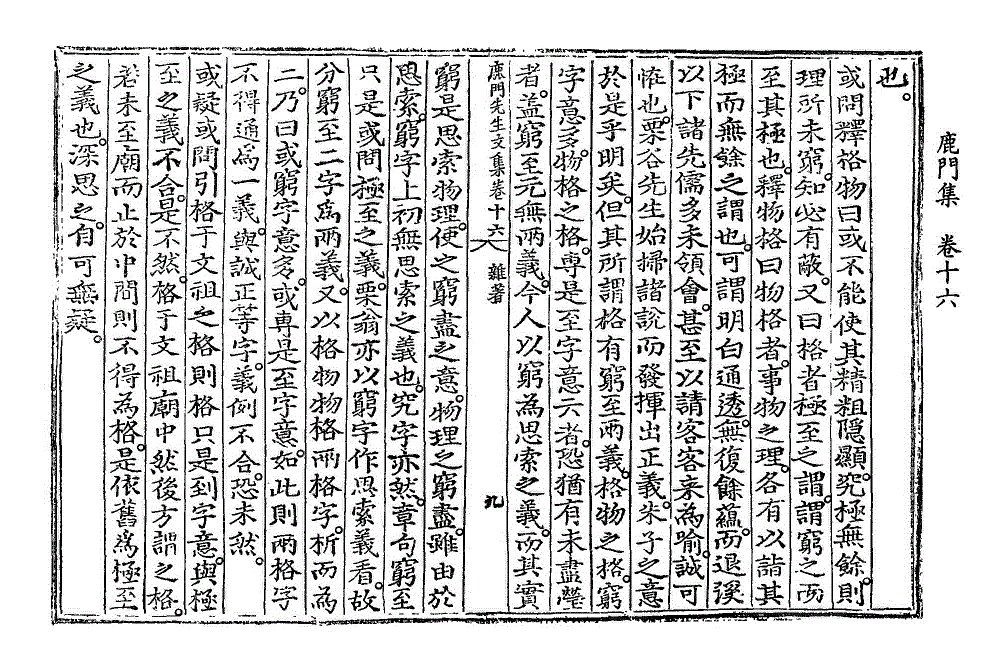 也。
也。或问释格物曰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馀。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又曰格者极至之谓。谓穷之而至其极也。释物格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之谓也。可谓明白通透。无复馀蕴。而退溪以下诸先儒多未领会。甚至以请客客来为喻。诚可怪也。栗谷先生始扫诸说而发挥出正义。朱子之意于是乎明矣。但其所谓格有穷至两义。格物之格。穷字意多。物格之格。专是至字意云者。恐犹有未尽莹者。盖穷至元无两义。今人以穷为思索之义。而其实穷是思索物理。使之穷尽之意。物理之穷尽。虽由于思索。穷字上初无思索之义也。究字亦然。章句穷至只是或问极至之义。栗翁亦以穷字作思索义看。故分穷至二字为两义。又以格物物格两格字。析而为二。乃曰或穷字意多。或专是至字意。如此则两格字不得通为一义。与诚正等字。义例不合。恐未然。
或疑或问引格于文祖之格则格只是到字意。与极至之义不合。是不然。格于文祖庙中然后方谓之格。若未至庙而止于中间则不得为格。是依旧为极至之义也。深思之。自可无疑。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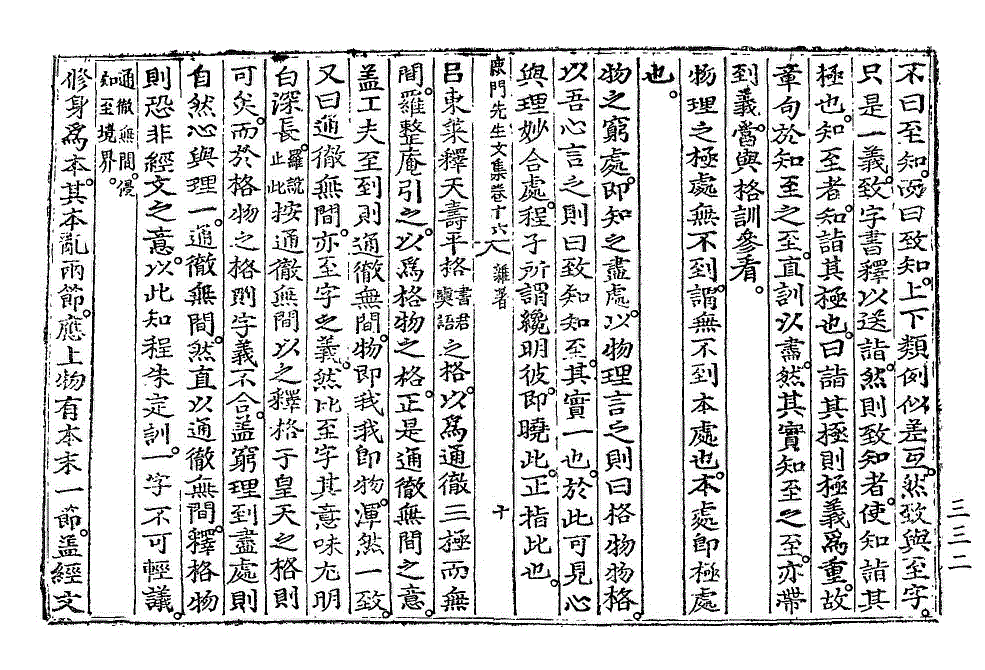 不曰至知。而曰致知。上下类例似差互。然致与至字。只是一义。致字书释以送诣。然则致知者。使知诣其极也。知至者。知诣其极也。曰诣其极则极义为重。故章句于知至之至。直训以尽。然其实知至之至。亦带到义。当与格训参看。
不曰至知。而曰致知。上下类例似差互。然致与至字。只是一义。致字书释以送诣。然则致知者。使知诣其极也。知至者。知诣其极也。曰诣其极则极义为重。故章句于知至之至。直训以尽。然其实知至之至。亦带到义。当与格训参看。物理之极处无不到。谓无不到本处也。本处即极处也。
物之穷处。即知之尽处。以物理言之则曰格物物格。以吾心言之则曰致知知至。其实一也。于此可见心与理妙合处。程子所谓才明彼。即晓此。正指此也。
吕东莱释天寿平格(书君奭语)之格。以为通彻三极而无间。罗整庵引之。以为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又曰通彻无间。亦至字之义。然比至字其意味尤明白深长。(罗说止此)按通彻无间以之释格于皇天之格则可矣。而于格物之格则字义不合。盖穷理到尽处则自然心与理一。通彻无间。然直以通彻无间。释格物则恐非经文之意。以此知程朱定训。一字不可轻议。(通彻无间。侵知至境界。)
修身为本。其本乱两节。应上物有本末一节。盖经文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3H 页
 有前后两段。后段即前段之注脚。故其语意呼应。文字起结。一一相符。正不可草率看。
有前后两段。后段即前段之注脚。故其语意呼应。文字起结。一一相符。正不可草率看。传首章
顾諟天之明命。或问云其全体大用。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所谓发见。不但指人心善端之发见。如手当恭足当重。父当慈子当孝。老者当安少者当怀。牛当穿鼻。马当络首。凡事物当然之则。或因事而呈露。或随物而昭著者。莫非吾明德之所具。而不待此心之感动。常常发见于面前。学者当随处精察而常目在之也。发见二字。当合此二者而言之。若专以人心善端看则却恐孤单。意味不长。
顾諟二字。包涵得无限意思。如穷理力行存养省察。皆在其中。而约而言之则只是一个敬。
传二章
盘铭一节。接上章自明。而易明为新。意承上而文起下。文字又浑圆绝无罅缝。可谓妙矣。
作新民释作振起其自新之民。盖谓人君若自新则民亦兴起而自新。故就此而又鼓舞振起以作成之也。意则诚完备。然或恐伤巧。愚意虽从康诰本文释以作新其民。民之自新之意。亦自包在其中。不必用断章取义之例。释以自新之民然后为得也。
或问则直用康诰本文以作新为说。此非与章句有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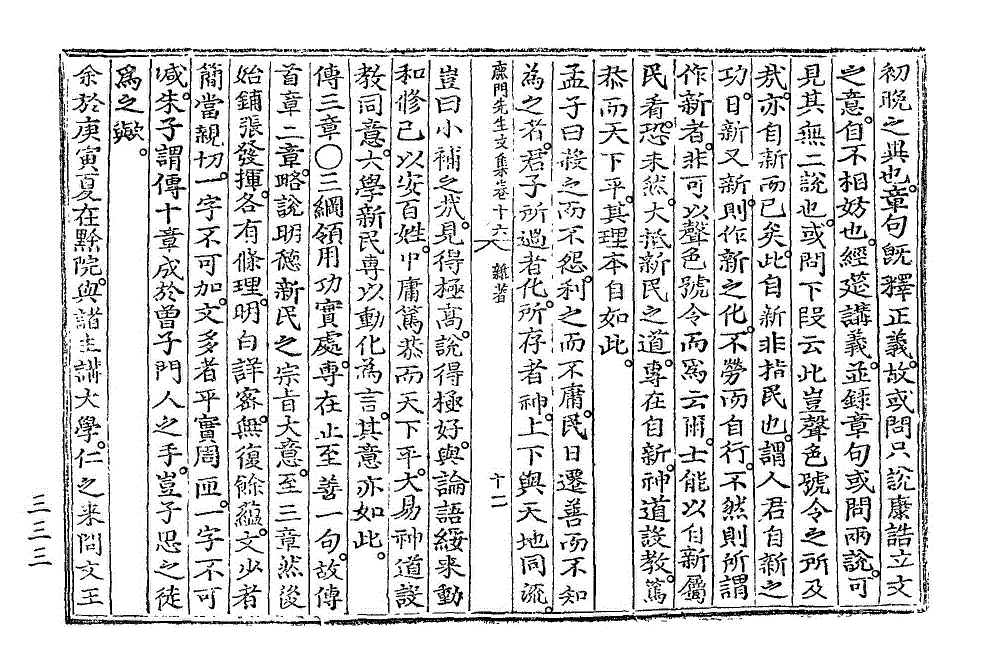 初晚之异也。章句既释正义。故或问只说康诰立文之意。自不相妨也。经筵讲义。并录章句或问两说。可见其无二说也。或问下段云此岂声色号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此自新非指民也。谓人君自新之功。日新又新。则作新之化。不劳而自行。不然则所谓作新者。非可以声色号令而为云尔。士能以自新属民看。恐未然。大抵新民之道。专在自新。神道设教。笃恭而天下平。其理本自如此。
初晚之异也。章句既释正义。故或问只说康诰立文之意。自不相妨也。经筵讲义。并录章句或问两说。可见其无二说也。或问下段云此岂声色号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此自新非指民也。谓人君自新之功。日新又新。则作新之化。不劳而自行。不然则所谓作新者。非可以声色号令而为云尔。士能以自新属民看。恐未然。大抵新民之道。专在自新。神道设教。笃恭而天下平。其理本自如此。孟子曰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见得极高。说得极好。与论语绥来动和修己以安百姓。中庸笃恭而天下平。大易神道设教同意。大学新民专以动化为言。其意亦如此。
传三章
三纲领用功实处。专在止至善一句。故传首章二章。略说明德新民之宗旨大意。至三章然后始铺张发挥。各有条理。明白详密。无复馀蕴。文少者简当亲切。一字不可加。文多者平实周匝。一字不可减。朱子谓传十章成于曾子门人之手。岂子思之徒为之欤。
余于庚寅夏在黔院。与诸生讲大学。仁之来问文王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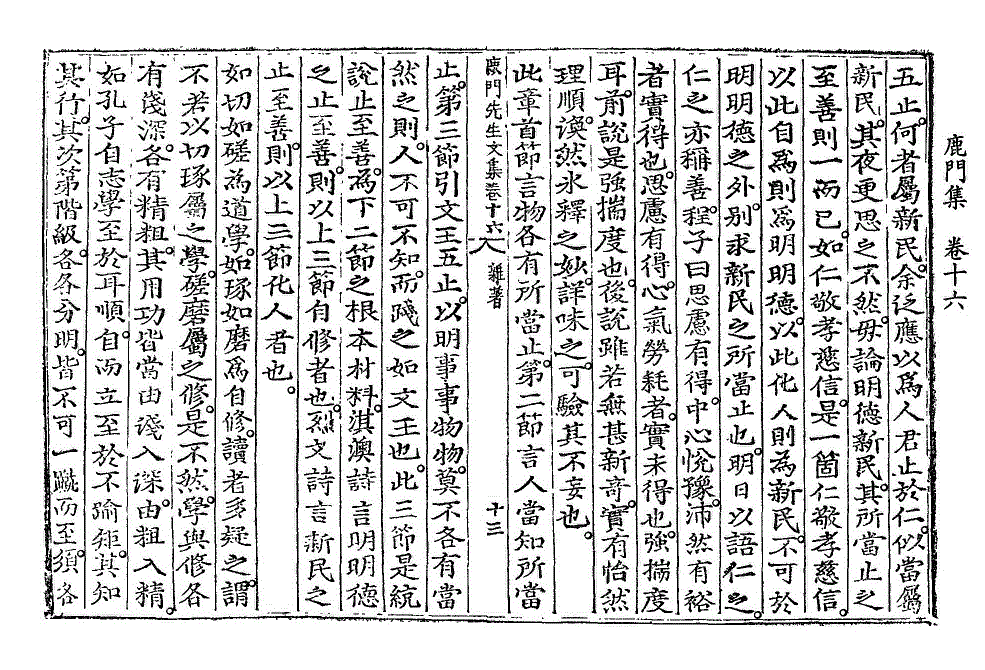 五止。何者属新民。余泛应以为人君止于仁。似当属新民。其夜更思之不然。毋论明德新民。其所当止之至善则一而已。如仁敬孝慈信。是一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为则为明明德。以此化人则为新民。不可于明明德之外。别求新民之所当止也。明日以语仁之。仁之亦称善。程子曰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前说是强揣度也。后说虽若无甚新奇。实有怡然理顺。涣然冰释之妙。详味之。可验其不妄也。
五止。何者属新民。余泛应以为人君止于仁。似当属新民。其夜更思之不然。毋论明德新民。其所当止之至善则一而已。如仁敬孝慈信。是一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为则为明明德。以此化人则为新民。不可于明明德之外。别求新民之所当止也。明日以语仁之。仁之亦称善。程子曰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前说是强揣度也。后说虽若无甚新奇。实有怡然理顺。涣然冰释之妙。详味之。可验其不妄也。此章首节言物各有所当止。第二节言人当知所当止。第三节引文王五止。以明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人不可不知。而践之如文王也。此三节是统说止至善。为下二节之根本材料。淇澳诗言明明德之止至善。则以上三节自修者也。烈文诗言新民之止至善。则以上三节化人者也。
如切如磋为道学。如琢如磨为自修。读者多疑之。谓不若以切琢属之学。磋磨属之修。是不然。学与修各有浅深。各有精粗。其用功皆当由浅入深。由粗入精。如孔子自志学至于耳顺。自而立至于不踰矩。其知其行。其次第阶级。各各分明。皆不可一蹴而至。须各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4L 页
 用一生功夫。循序渐进然后可也。今若以切琢属学。磋磨属修。则知专为浅与粗。行专为深与精。其取譬不衬切。深究之可见。若其以骨角属学。玉石属修。则或问所谓脉理可寻而切磋之功易。浑全坚确而琢磨之功难云者。尽之矣。
用一生功夫。循序渐进然后可也。今若以切琢属学。磋磨属修。则知专为浅与粗。行专为深与精。其取譬不衬切。深究之可见。若其以骨角属学。玉石属修。则或问所谓脉理可寻而切磋之功易。浑全坚确而琢磨之功难云者。尽之矣。新民一事。其精神鼓发。专在自新。而若其成就结裹则又在絜矩。非自新则固无以兴起亿兆之善心。而行匡直辅翼之化矣。非絜矩则又何以使民各遂其兴起之善心。而尽亲亲长长之道乎。故二章专以自新为主。而至此三章则又极言亲贤乐利之效。以明新民之止至善。乃在于此也。盖贤其贤亲其亲者。自新之馀化也。乐其乐利其利者。絜矩之遗泽也。民之感发迁善。虽由自新。而至其安生乐业。欲孝者尽其孝。欲弟者尽其弟。欲慈者尽其慈。而无一物不得其所。则实由乎人君与民。同好恶而尽絜矩之道也。旧疑大学新民。虽略说作新及兴孝兴弟不倍。而其反复铺张。专在絜矩。与新字不合。虽强说得通。而终未快活。今乃见其新民极功。正在絜矩。而亲贤乐利。即是新民之所以止于至善者也。
自新以化之。絜矩以成之。新民之极功备矣。若其学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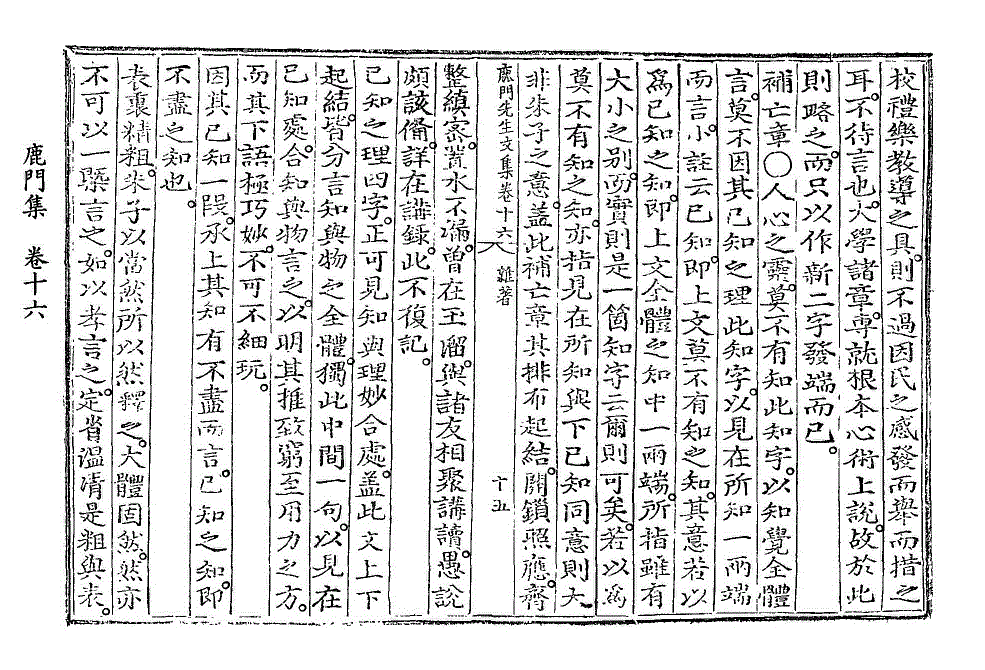 校礼乐教导之具。则不过因民之感发而举而措之耳。不待言也。大学诸章。专就根本心术上说。故于此则略之。而只以作新二字发端而已。
校礼乐教导之具。则不过因民之感发而举而措之耳。不待言也。大学诸章。专就根本心术上说。故于此则略之。而只以作新二字发端而已。补亡章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知字。以知觉全体言。莫不因其已知之理此知字。以见在所知一两端而言。小注云已知。即上文莫不有知之知。其意若以为已知之知。即上文全体之知中一两端。所指虽有大小之别。而实则是一个知字云尔则可矣。若以为莫不有知之知。亦指见在所知与下已知同意则大非朱子之意。盖此补亡章其排布起结。关锁照应。齐整缜密。置水不漏。曾在玉溜。与诸友相聚讲读。愚说颇该备。详在讲录。此不复记。
已知之理四字。正可见知与理妙合处。盖此文上下起结。皆分言知与物之全体。独此中间一句。以见在已知处。合知与物言之。以明其推致穷至用力之方。而其下语极巧妙。不可不细玩。
因其已知一段。承上其知有不尽而言。已知之知。即不尽之知也。
表里精粗。朱子以当然所以然释之。大体固然。然亦不可以一槩言之。如以孝言之。定省温凊。是粗与表。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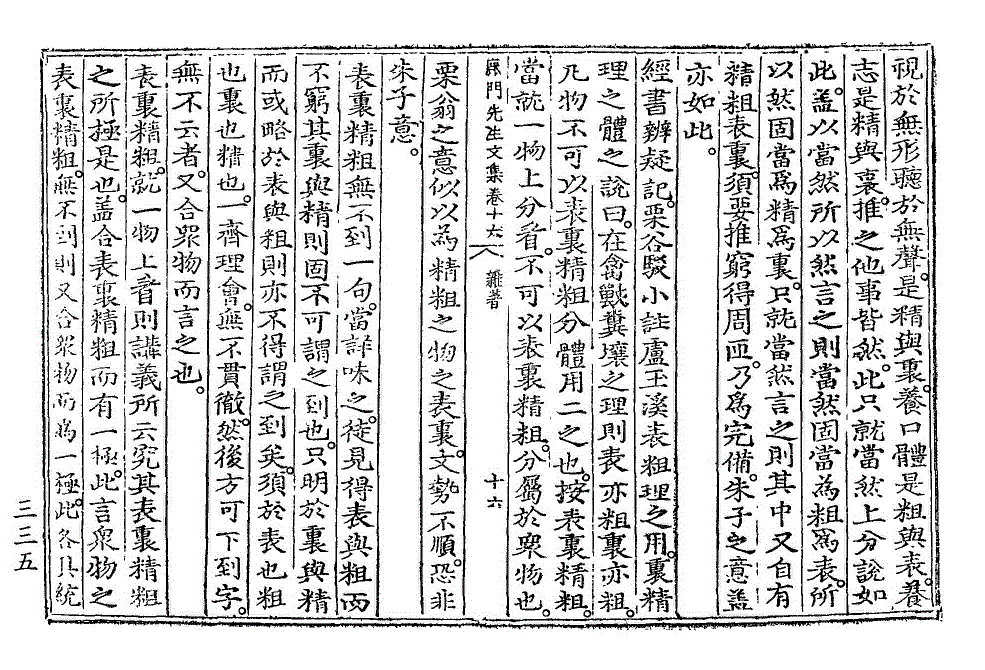 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是精与里。养口体是粗与表。养志是精与里。推之他事皆然。此只就当然上分说如此。盖以当然所以然言之则当然固当为粗为表。所以然固当为精为里。只就当然言之则其中又自有精粗表里。须要推穷得周匝。乃为完备。朱子之意盖亦如此。
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是精与里。养口体是粗与表。养志是精与里。推之他事皆然。此只就当然上分说如此。盖以当然所以然言之则当然固当为粗为表。所以然固当为精为里。只就当然言之则其中又自有精粗表里。须要推穷得周匝。乃为完备。朱子之意盖亦如此。经书辨疑记。栗谷驳小注卢玉溪表粗理之用。里精理之体之说曰。在禽兽粪壤之理则表亦粗里亦粗。凡物不可以表里精粗分体用二之也。按表里精粗。当就一物上分看。不可以表里精粗。分属于众物也。栗翁之意似以为精粗之物之表里。文势不顺。恐非朱子意。
表里精粗无不到一句。当详味之。徒见得表与粗而不穷其里与精则固不可谓之到也。只明于里与精。而或略于表与粗则亦不得谓之到矣。须于表也粗也里也精也。一齐理会。无不贯彻。然后方可下到字。无不云者。又合众物而言之也。
表里精粗。就一物上看则讲义所云究其表里精粗之所极是也。盖合表里精粗而有一极。此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则又合众物而为一极。此各具统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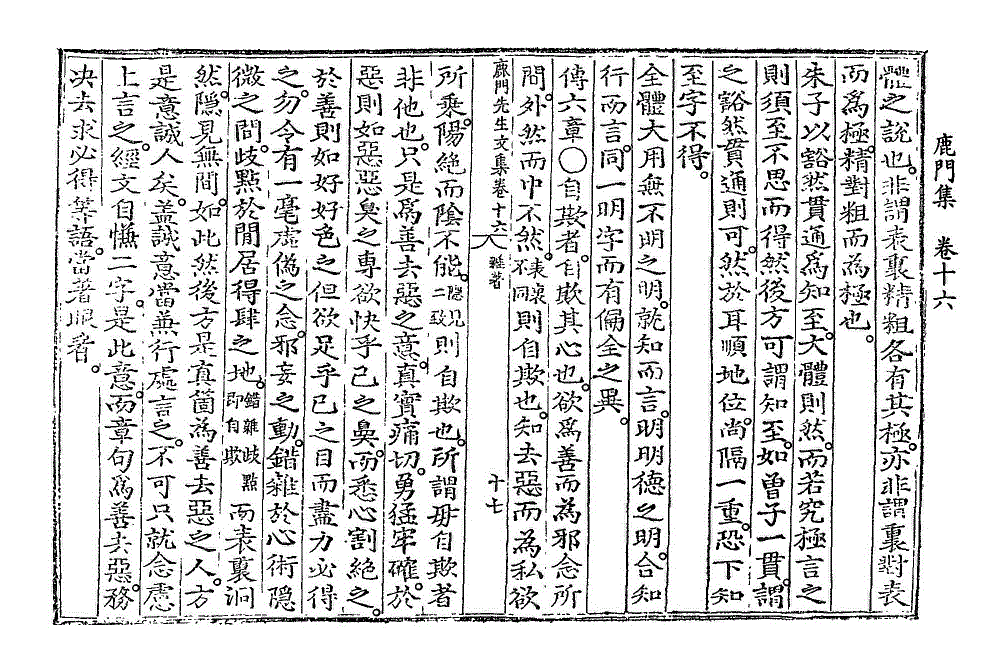 体之说也。非谓表里精粗各有其极。亦非谓里对表而为极。精对粗而为极也。
体之说也。非谓表里精粗各有其极。亦非谓里对表而为极。精对粗而为极也。朱子以豁然贯通为知至。大体则然。而若究极言之则须至不思而得然后方可谓知至。如曾子一贯。谓之豁然贯通则可。然于耳顺地位。尚隔一重。恐下知至字不得。
全体大用无不明之明。就知而言。明明德之明。合知行而言。同一明字而有偏全之异。
传六章
自欺者。自欺其心也。欲为善而为邪念所间。外然而中不然。(表里不同)则自欺也。知去恶而为私欲所乘。阳绝而阴不能。(隐见二致)则自欺也。所谓毋自欺者非他也。只是为善去恶之意。真实痛切。勇猛牢确。于恶则如恶恶臭之专欲快乎己之鼻。而悉心割绝之。于善则如好好色之但欲足乎己之目而尽力必得之。勿令有一毫虚伪之念。邪妄之动。错杂于心术隐微之间。歧点于閒居得肆之地。(错杂歧点即自欺)而表里洞然。隐见无间。如此然后方是真个为善去恶之人。方是意诚人矣。盖诚意当兼行处言之。不可只就念虑上言之。经文自慊二字。是此意。而章句为善去恶。务决去求必得等语。当著眼看。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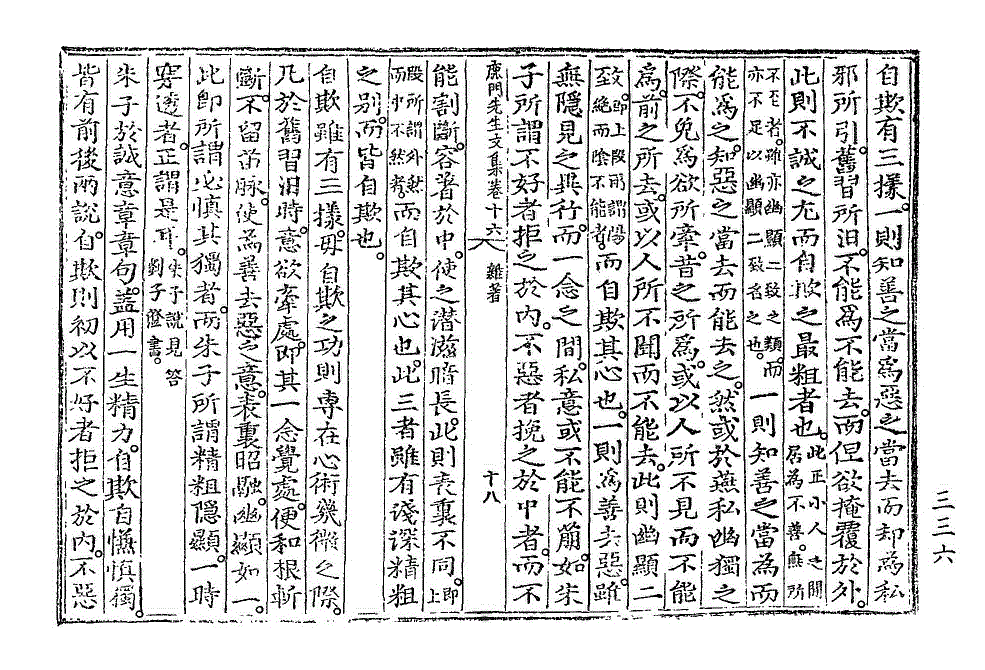 自欺有三㨾。一则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而却为私邪所引。旧习所汨。不能为不能去。而但欲掩覆于外。此则不诚之尤而自欺之最粗者也。(此正小人之閒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者。虽亦幽显二致之类。而亦不足以幽显二致名之也。)一则知善之当为而能为之。知恶之当去而能去之。然或于燕私幽独之际。不免为欲所牵。昔之所为。或以人所不见而不能为。前之所去。或以人所不闻而不能去。此则幽显二致。(即上段所谓阳绝而阴不能者。)而自欺其心也。一则为善去恶。虽无隐见之异行。而一念之间。私意或不能不萌。如朱子所谓不好者拒之于内。不恶者挽之于中者。而不能割断。容著于中。使之潜滋暗长。此则表里不同。(即上段所谓外然而中不然者。)而自欺其心也。此三者虽有浅深精粗之别。而皆自欺也。
自欺有三㨾。一则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而却为私邪所引。旧习所汨。不能为不能去。而但欲掩覆于外。此则不诚之尤而自欺之最粗者也。(此正小人之閒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者。虽亦幽显二致之类。而亦不足以幽显二致名之也。)一则知善之当为而能为之。知恶之当去而能去之。然或于燕私幽独之际。不免为欲所牵。昔之所为。或以人所不见而不能为。前之所去。或以人所不闻而不能去。此则幽显二致。(即上段所谓阳绝而阴不能者。)而自欺其心也。一则为善去恶。虽无隐见之异行。而一念之间。私意或不能不萌。如朱子所谓不好者拒之于内。不恶者挽之于中者。而不能割断。容著于中。使之潜滋暗长。此则表里不同。(即上段所谓外然而中不然者。)而自欺其心也。此三者虽有浅深精粗之别。而皆自欺也。自欺虽有三㨾。毋自欺之功则专在心术几微之际。凡于旧习汨时。意欲牵处。即其一念觉处。便和根斩断。不留苗脉。使为善去恶之意。表里昭融。幽显如一。此即所谓必慎其独者。而朱子所谓精粗隐显。一时穿透者。正谓是耳。(朱子说见答刘子澄书。)
朱子于诚意章章句。盖用一生精力。自欺自慊慎独。皆有前后两说。自欺则初以不好者拒之于内。不恶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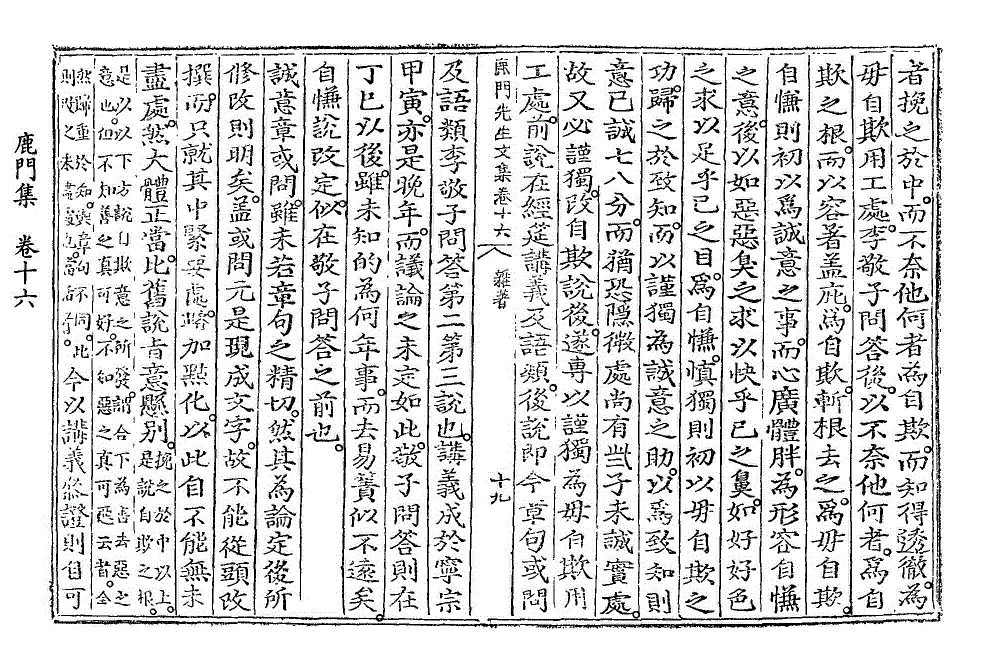 者挽之于中。而不奈他何者为自欺。而知得透彻。为毋自欺用工处。李敬子问答后。以不奈他何者。为自欺之根。而以容著盖庇。为自欺。斩根去之。为毋自欺。自慊则初以为诚意之事。而心广体胖。为形容自慊之意。后以如恶恶臭之求以快乎己之鼻。如好好色之求以足乎己之目。为自慊。慎独则初以毋自欺之功。归之于致知。而以谨独为诚意之助。以为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而犹恐隐微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又必谨独。改自欺说后。遂专以谨独为毋自欺用工处。前说在经筵讲义及语类。后说即今章句或问及语类李敬子问答第二第三说也。讲义成于宁宗甲寅。亦是晚年。而议论之未定如此。敬子问答则在丁巳以后。虽未知的为何年事。而去易箦似不远矣。自慊说改定。似在敬子问答之前也。
者挽之于中。而不奈他何者为自欺。而知得透彻。为毋自欺用工处。李敬子问答后。以不奈他何者。为自欺之根。而以容著盖庇。为自欺。斩根去之。为毋自欺。自慊则初以为诚意之事。而心广体胖。为形容自慊之意。后以如恶恶臭之求以快乎己之鼻。如好好色之求以足乎己之目。为自慊。慎独则初以毋自欺之功。归之于致知。而以谨独为诚意之助。以为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而犹恐隐微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又必谨独。改自欺说后。遂专以谨独为毋自欺用工处。前说在经筵讲义及语类。后说即今章句或问及语类李敬子问答第二第三说也。讲义成于宁宗甲寅。亦是晚年。而议论之未定如此。敬子问答则在丁巳以后。虽未知的为何年事。而去易箦似不远矣。自慊说改定。似在敬子问答之前也。诚意章或问。虽未若章句之精切。然其为论定后所修改则明矣。盖或问元是现成文字。故不能从头改撰。而只就其中紧要处。略加点化。以此自不能无未尽处。然大体正当。比旧说旨意悬别。(挽之于中以上。是说自欺之根。是以以下方说自欺意之所发。谓合下为善去恶之意也。但不知善之真可好。不知恶之真可恶云者。全然归重于知。与章句不同。此则改之未尽处也。当活看。)今以讲义参證则自可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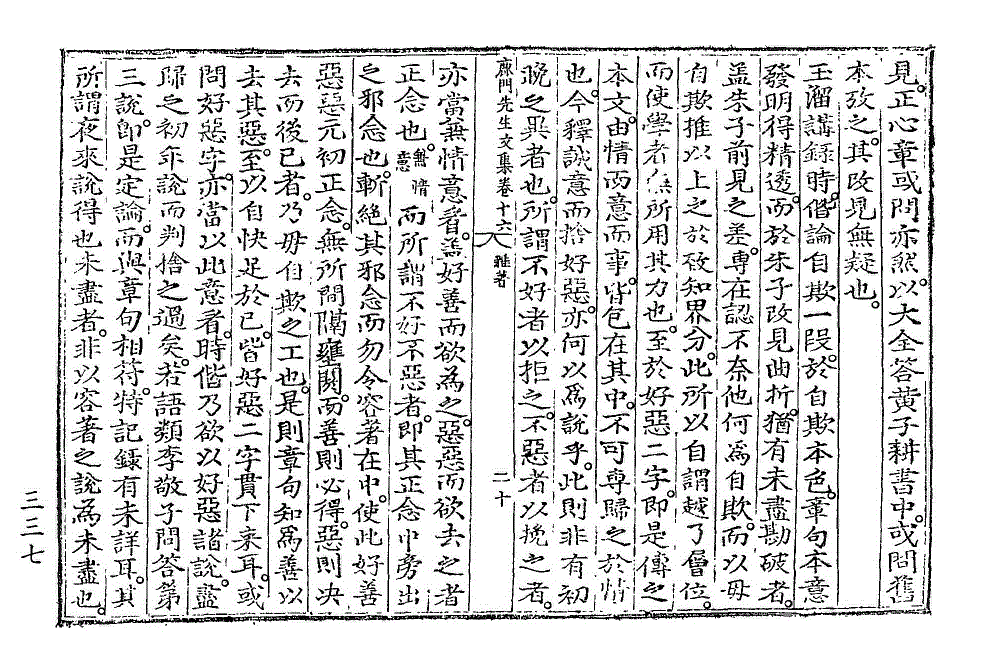 见。正心章或问亦然。以大全答黄子耕书中。或问旧本考之。其改见无疑也。
见。正心章或问亦然。以大全答黄子耕书中。或问旧本考之。其改见无疑也。玉溜讲录时。偕论自欺一段。于自欺本色。章句本意发明得精透。而于朱子改见曲折。犹有未尽勘破者。盖朱子前见之差。专在认不奈他何为自欺。而以毋自欺推以上之于致知界分。此所以自谓越了层位。而使学者无所用其力也。至于好恶二字。即是传之本文。由情而意而事。皆包在其中。不可专归之于情也。今释诚意而舍好恶。亦何以为说乎。此则非有初晚之异者也。所谓不好者以拒之。不恶者以挽之者。亦当兼情意看。盖好善而欲为之。恶恶而欲去之者正念也。(兼情意。)而所谓不好不恶者。即其正念中旁出之邪念也。斩绝其邪念而勿令容著在中。使此好善恶恶元初正念。无所间隔壅阏。而善则必得。恶则决去而后已者。乃毋自欺之工也。是则章句知为善以去其恶。至以自快足于己。皆好恶二字贯下来耳。或问好恶字。亦当以此意看。时偕乃欲以好恶诸说。尽归之初年说而判舍之过矣。若语类李敬子问答第三说。即是定论。而与章句相符。特记录有未详耳。其所谓夜来说得也未尽者。非以容著之说为未尽也。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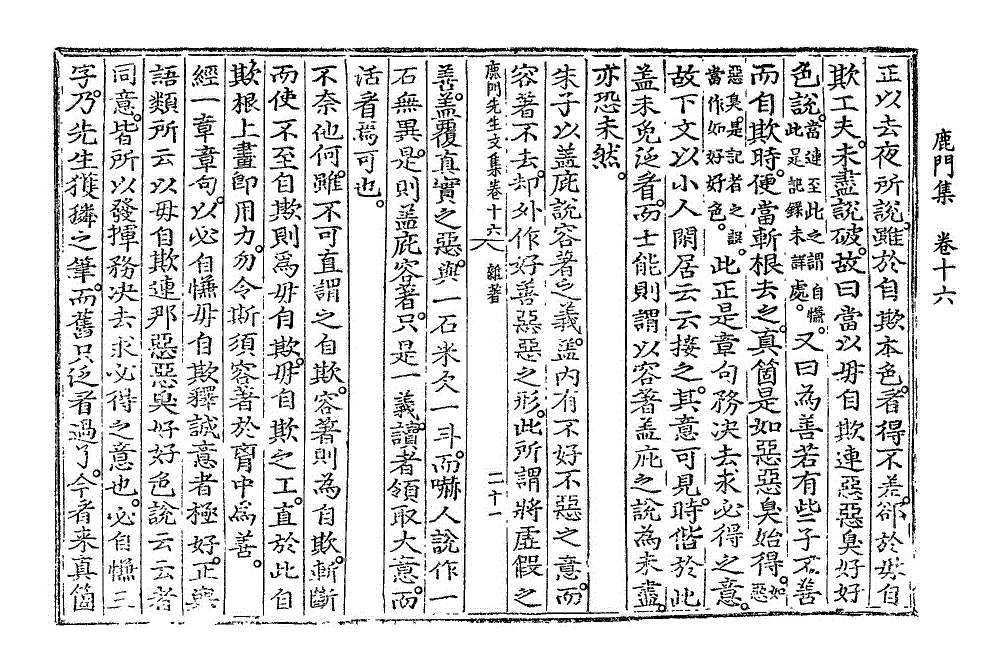 正以去夜所说。虽于自欺本色。看得不差。郤于毋自欺工夫。未尽说破。故曰当以毋自欺连恶恶臭好好色说。(当连至此之谓自慊。此是记录未详处。)又曰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恶恶臭。是记者之误。当作如好好色。)此正是章句务决去求必得之意。故下文以小人闲居云云接之。其意可见。时偕于此盖未免泛看。而士能则谓以容著盖庇之说为未尽。亦恐未然。
正以去夜所说。虽于自欺本色。看得不差。郤于毋自欺工夫。未尽说破。故曰当以毋自欺连恶恶臭好好色说。(当连至此之谓自慊。此是记录未详处。)又曰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恶恶臭。是记者之误。当作如好好色。)此正是章句务决去求必得之意。故下文以小人闲居云云接之。其意可见。时偕于此盖未免泛看。而士能则谓以容著盖庇之说为未尽。亦恐未然。朱子以盖庇说容著之义。盖内有不好不恶之意。而容著不去。却外作好善恶恶之形。此所谓将虚假之善。盖覆真实之恶。与一石米欠一斗。而吓人说作一石无异。是则盖庇容著。只是一义。读者领取大意。而活看焉可也。
不奈他何。虽不可直谓之自欺。容著则为自欺。斩断而使不至自欺则为毋自欺。毋自欺之工。直于此自欺根上画即用力。勿令斯须容著于胸中为善。
经一章章句。以必自慊毋自欺释诚意者极好。正与语类所云以毋自欺连那恶恶臭好好色说云云者同意。皆所以发挥务决去求必得之意也。必自慊三字。乃先生获麟之笔。而旧只泛看过了。今看来真个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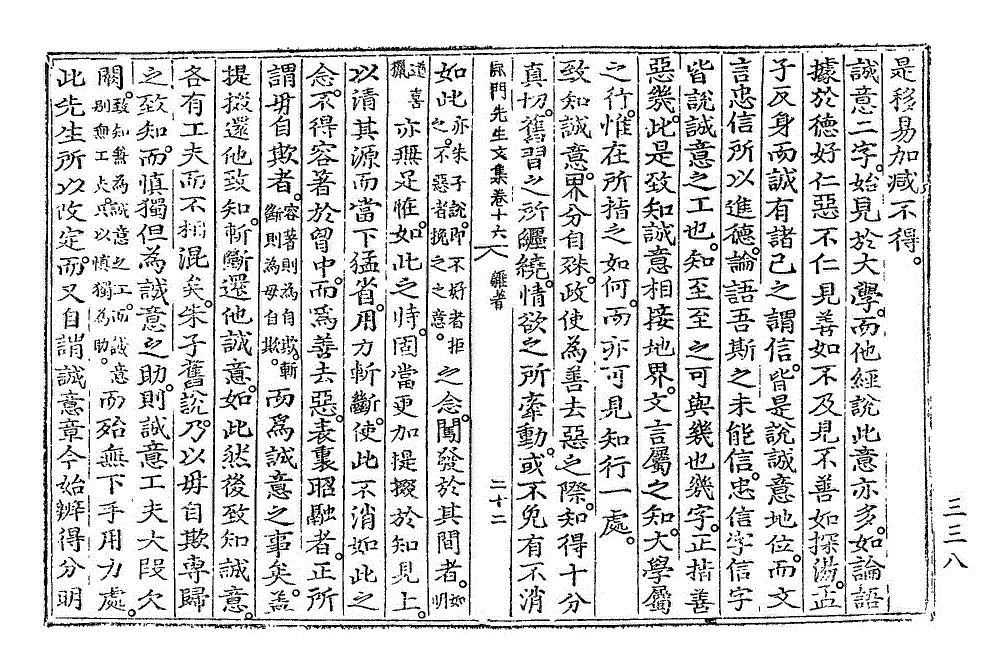 是移易加减不得。
是移易加减不得。诚意二字。始见于大学。而他经说此意亦多。如论语据于德好仁恶不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孟子反身而诚有诸己之谓信。皆是说诚意地位。而文言忠信所以进德。论语吾斯之未能信。忠信字信字皆说诚意之工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几字。正指善恶几。此是致知诚意相接地界。文言属之知。大学属之行。惟在所指之如何。而亦可见知行一处。
致知诚意。界分自殊。政使为善去恶之际。知得十分真切。旧习之所缠绕。情欲之所牵动。或不免有不消如此(亦朱子说。即不好者拒之。不恶者挽之之意。)之念。闯发于其间者。(如明道喜猎)亦无足怪。如此之时。固当更加提掇于知见上。以清其源而当下猛省。用力斩断。使此不消如此之念。不得容著于胸中。而为善去恶。表里昭融者。正所谓毋自欺者。(容著则为自欺。斩断则为毋自欺。)而为诚意之事矣。盖提掇还他致知。斩断还他诚意。如此然后致知诚意。各有工夫而不相混矣。朱子旧说。乃以毋自欺专归之致知。而慎独但为诚意之助。则诚意工夫大段欠阙。(致知兼为诚意之工。而诚意别无工夫。只以慎独为助。)而殆无下手用力处。此先生所以改定。而又自谓诚意章今始辨得分明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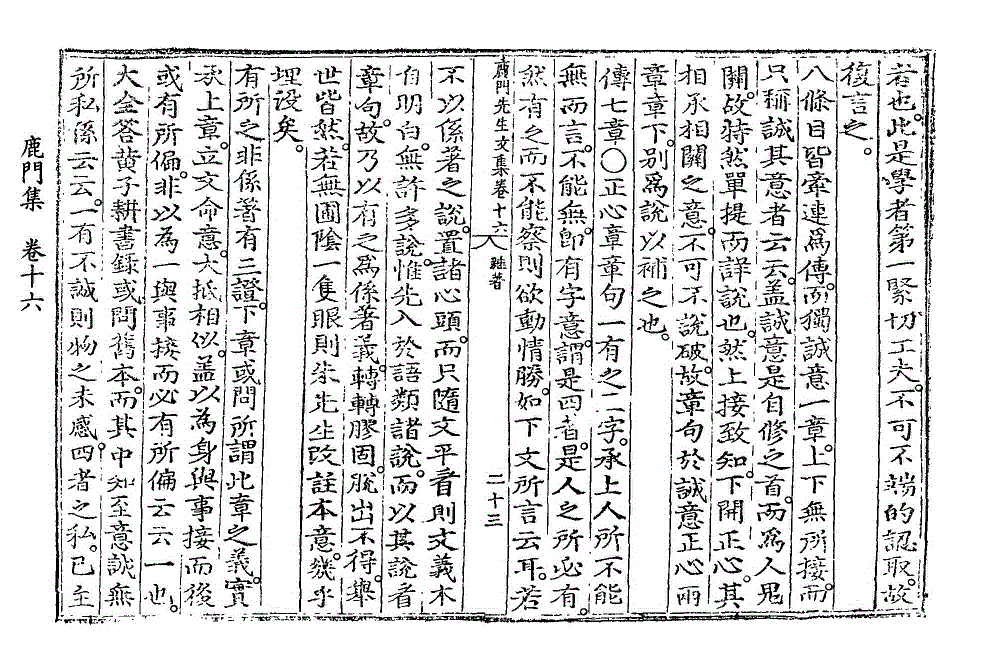 者也。此是学者第一紧切工夫。不可不端的认取。故复言之。
者也。此是学者第一紧切工夫。不可不端的认取。故复言之。八条目皆牵连为传。而独诚意一章。上下无所接。而只称诚其意者云云。盖诚意是自修之首。而为人鬼关。故特然单提而详说也。然上接致知。下开正心。其相承相关之意。不可不说破。故章句于诚意正心两章章下。别为说以补之也。
传七章
正心章章句一有之二字。承上人所不能无而言。不能无。即有字意。谓是四者。是人之所必有。然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如下文所言云耳。若不以系著之说。置诸心头。而只随文平看则文义本自明白。无许多说。惟先入于语类诸说。而以其说看章句。故乃以有之为系著义。转转胶固。脱出不得。举世皆然。若无圃阴一只眼则朱先生改注本意。几乎埋没矣。
有所之非系著有三證。下章或问所谓此章之义。实承上章。立文命意。大抵相似。盖以为身与事接而后或有所偏。非以为一与事接而必有所偏云云一也。大全答黄子耕书录或问旧本。而其中知至意诚无所私系云云。一有不诚则物之未感。四者之私。已主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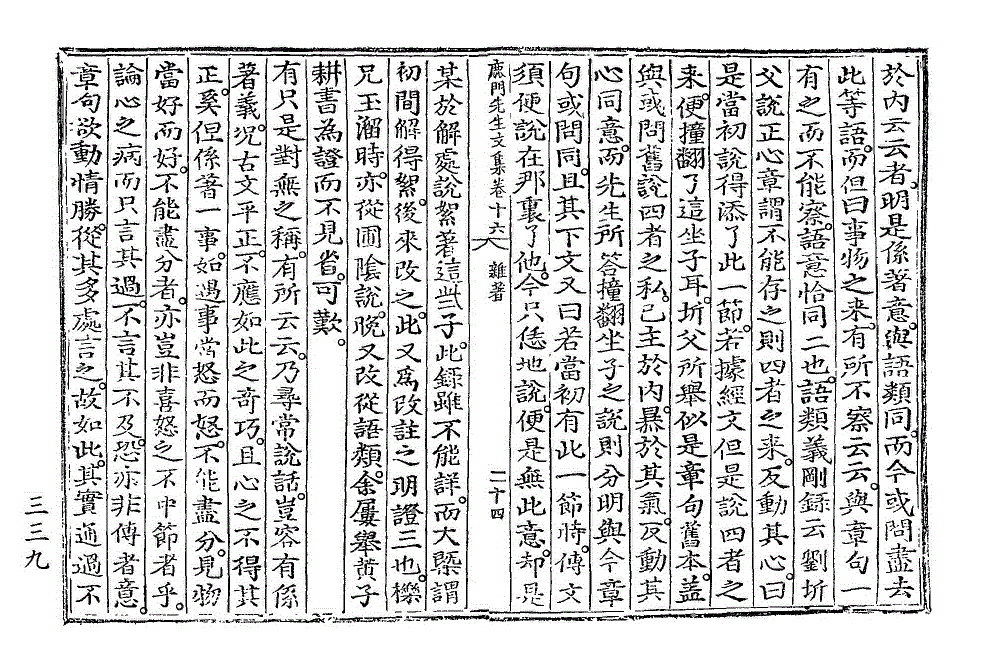 于内云云者。明是系著意。与语类同。而今或问尽去此等语。而但曰事物之来。有所不察云云。与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语意恰同二也。语类义刚录云刘圻父说正心章谓不能存之则四者之来。反动其心。曰是当初说得添了此一节。若据经文但是说四者之来。便撞翻了这坐子耳。圻父所举似是章句旧本。盖与或问旧说四者之私。已主于内。暴于其气。反动其心同意。而先生所答撞翻坐子之说则分明与今章句或问同。且其下文又曰若当初有此一节时。传文须便说在那里了他。今只恁地说。便是无此意。却是某于解处说絮著这些子。此录虽不能详。而大槩谓初间解得絮。后来改之。此又为改注之明證三也。栎兄玉溜时。亦从圃阴说。晚又改从语类。余屡举黄子耕书为證而不见省。可叹。
于内云云者。明是系著意。与语类同。而今或问尽去此等语。而但曰事物之来。有所不察云云。与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语意恰同二也。语类义刚录云刘圻父说正心章谓不能存之则四者之来。反动其心。曰是当初说得添了此一节。若据经文但是说四者之来。便撞翻了这坐子耳。圻父所举似是章句旧本。盖与或问旧说四者之私。已主于内。暴于其气。反动其心同意。而先生所答撞翻坐子之说则分明与今章句或问同。且其下文又曰若当初有此一节时。传文须便说在那里了他。今只恁地说。便是无此意。却是某于解处说絮著这些子。此录虽不能详。而大槩谓初间解得絮。后来改之。此又为改注之明證三也。栎兄玉溜时。亦从圃阴说。晚又改从语类。余屡举黄子耕书为證而不见省。可叹。有只是对无之称。有所云云。乃寻常说话。岂容有系著义。况古文平正。不应如此之奇巧。且心之不得其正。奚但系著一事。如遇事当怒而怒。不能尽分。见物当好而好。不能尽分者。亦岂非喜怒之不中节者乎。论心之病而只言其过。不言其不及。恐亦非传者意。章句欲动情胜。从其多处言之。故如此。其实通过不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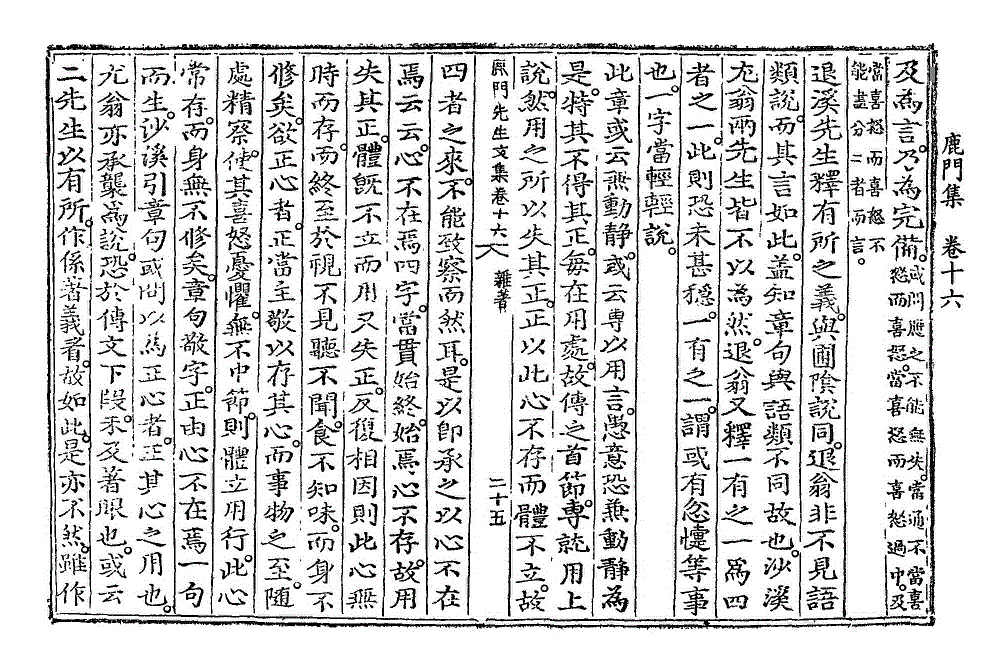 及为言。乃为完备。(或问应之不能无失。当通不当喜怒而喜怒。当喜怒而喜怒过中。及当喜怒而喜怒不能尽分二者而言。)
及为言。乃为完备。(或问应之不能无失。当通不当喜怒而喜怒。当喜怒而喜怒过中。及当喜怒而喜怒不能尽分二者而言。)退溪先生释有所之义。与圃阴说同。退翁非不见语类说。而其言如此。盖知章句与语类不同故也。沙溪尤翁两先生皆不以为然。退翁又释一有之一为四者之一。此则恐未甚稳。一有之一。谓或有忿懥等事也。一字当轻轻说。
此章或云兼动静。或云专以用言。愚意恐兼动静为是。特其不得其正。每在用处。故传之首节。专就用上说。然用之所以失其正。正以此心不存而体不立。故四者之来。不能致察而然耳。是以即承之以心不在焉云云。心不在焉四字。当贯始终。始焉心不存。故用失其正。体既不立而用又失正。反复相因则此心无时而存。而终至于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而身不修矣。欲正心者。正当主敬以存其心。而事物之至。随处精察。使其喜怒忧惧。无不中节。则体立用行。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矣。章句敬字。正由心不在焉一句而生。沙溪引章句或问以为正心者。正其心之用也。尤翁亦承袭为说。恐于传文下段。未及著眼也。或云二先生以有所。作系著义看。故如此。是亦不然。虽作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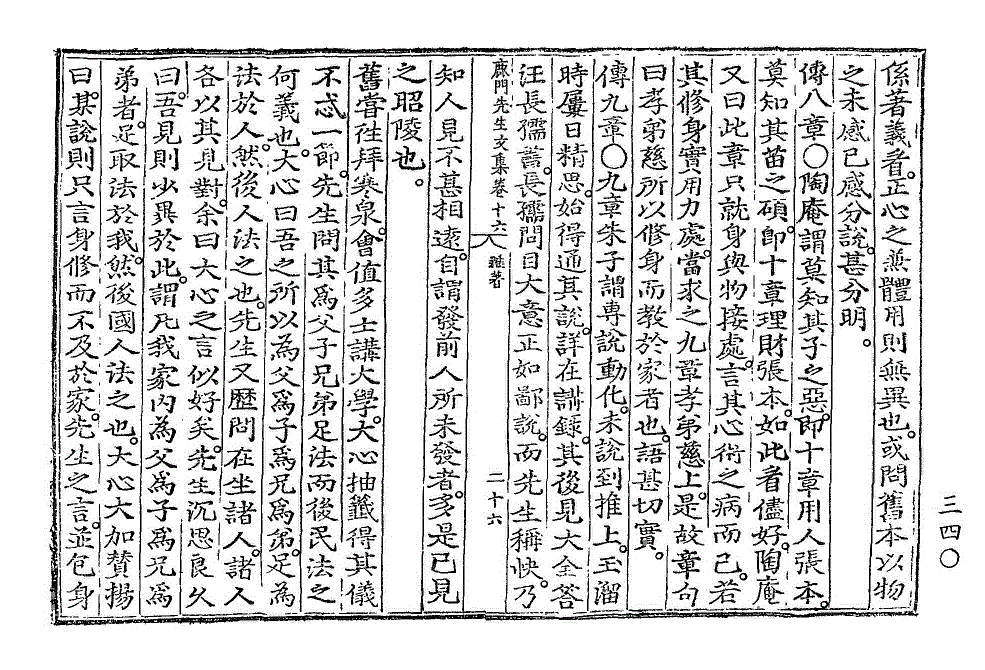 系著义看。正心之兼体用则无异也。或问旧本以物之未感已感分说。甚分明。
系著义看。正心之兼体用则无异也。或问旧本以物之未感已感分说。甚分明。传八章
陶庵谓莫知其子之恶。即十章用人张本。莫知其苗之硕。即十章理财张本。如此看尽好。陶庵又曰此章只就身与物接处。言其心术之病而已。若其修身实用力处。当求之九章孝弟慈上。是故章句曰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语甚切实。
传九章
九章朱子谓专说动化。未说到推上。玉溜时屡日精思。始得通其说。详在讲录。其后见大全答汪长孺书。长孺问目大意正如鄙说。而先生称快。乃知人见不甚相远。自谓发前人所未发者。多是己见之昭陵也。
旧尝往拜寒泉。会值多士讲大学。大心抽签得其仪不忒一节。先生问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何义也。大心曰吾之所以为父为子为兄为弟。足为法于人。然后人法之也。先生又历问在坐诸人。诸人各以其见对。余曰大心之言似好矣。先生沉思良久曰。吾见则少异于此。谓凡我家内为父为子为兄为弟者。足取法于我。然后国人法之也。大心大加赞扬曰。某说则只言身修而不及于家。先生之言。并包身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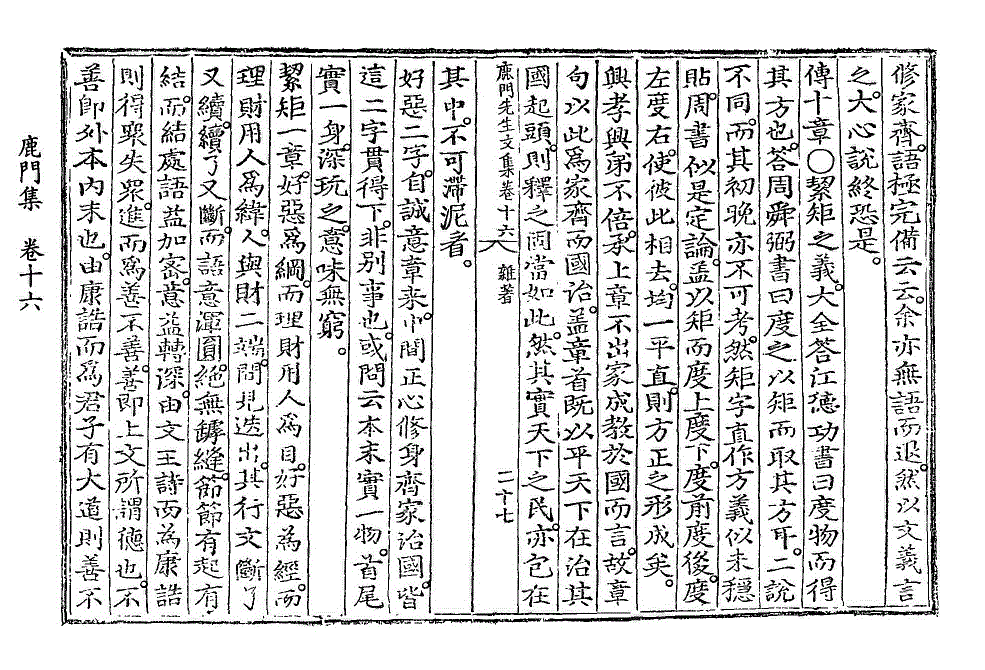 修家齐。语极完备云云。余亦无语而退。然以文义言之。大心说终恐是。
修家齐。语极完备云云。余亦无语而退。然以文义言之。大心说终恐是。传十章
絜矩之义。大全答江德功书曰度物而得其方也。答周舜弼书曰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二说不同。而其初晚亦不可考。然矩字直作方义似未稳贴。周书似是定论。盖以矩而度上度下。度前度后。度左度右。使彼此相去。均一平直。则方正之形成矣。
兴孝兴弟不倍。承上章不出家成教于国而言。故章句以此为家齐而国治。盖章首既以平天下在治其国起头。则释之固当如此。然其实天下之民。亦包在其中。不可滞泥看。
好恶二字。自诚意章来。中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皆这二字贯得下。非别事也。或问云本末实一物。首尾实一身。深玩之。意味无穷。
絜矩一章。好恶为纲。而理财用人为目。好恶为经。而理财用人为纬。人与财二端。间见迭出。其行文断了又续。续了又断。而语意浑圆。绝无罅缝。节节有起有结。而结处语益加密。意益转深。由文王诗而为康诰则得众失众。进而为善不善。善即上文所谓德也。不善即外本内末也。由康诰而为君子有大道则善不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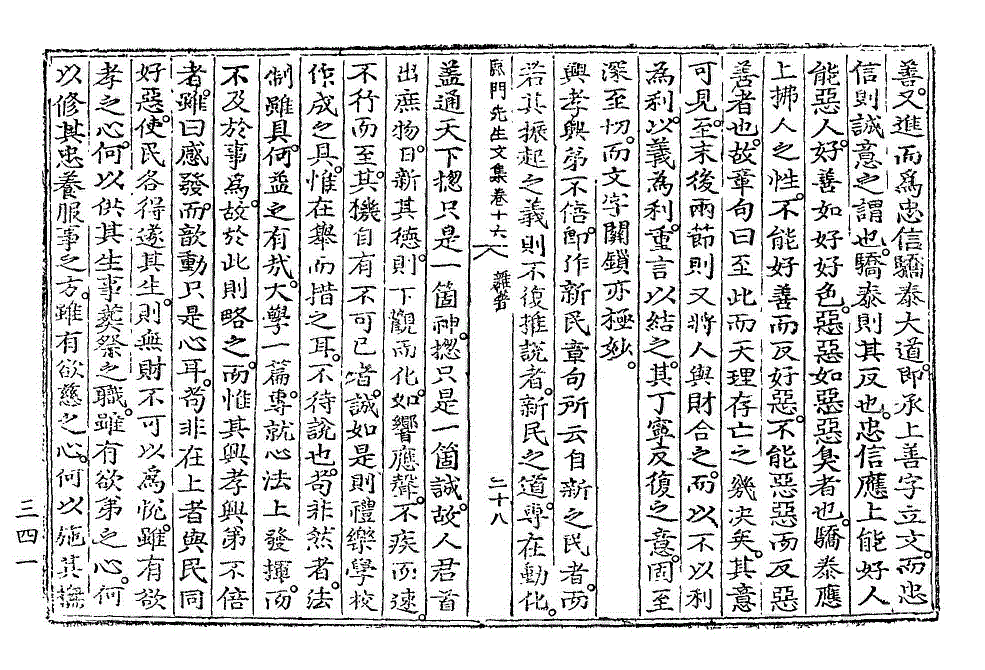 善。又进而为忠信骄泰大道。即承上善字立文。而忠信则诚意之谓也。骄泰则其反也。忠信应上能好人能恶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者也。骄泰应上拂人之性。不能好善而反好恶。不能恶恶而反恶善者也。故章句曰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其意可见。至末后两节则又将人与财合之。而以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重言以结之。其丁宁反复之意。固至深至切。而文字关锁亦极妙。
善。又进而为忠信骄泰大道。即承上善字立文。而忠信则诚意之谓也。骄泰则其反也。忠信应上能好人能恶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者也。骄泰应上拂人之性。不能好善而反好恶。不能恶恶而反恶善者也。故章句曰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其意可见。至末后两节则又将人与财合之。而以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重言以结之。其丁宁反复之意。固至深至切。而文字关锁亦极妙。兴孝兴弟不倍。即作新民章句所云自新之民者。而若其振起之义则不复推说者。新民之道。专在动化。盖通天下揔只是一个神。揔只是一个诚。故人君首出庶物。日新其德。则下观而化。如响应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机自有不可已者。诚如是则礼乐学校作成之具。惟在举而措之耳。不待说也。苟非然者。法制虽具。何益之有哉。大学一篇。专就心法上发挥。而不及于事为。故于此则略之。而惟其兴孝兴弟不倍者。虽曰感发。而歆动只是心耳。苟非在上者与民同好恶。使民各得遂其生。则无财不可以为悦。虽有欲孝之心。何以供其生事葬祭之职。虽有欲弟之心。何以修其忠养服事之方。虽有欲慈之心。何以施其抚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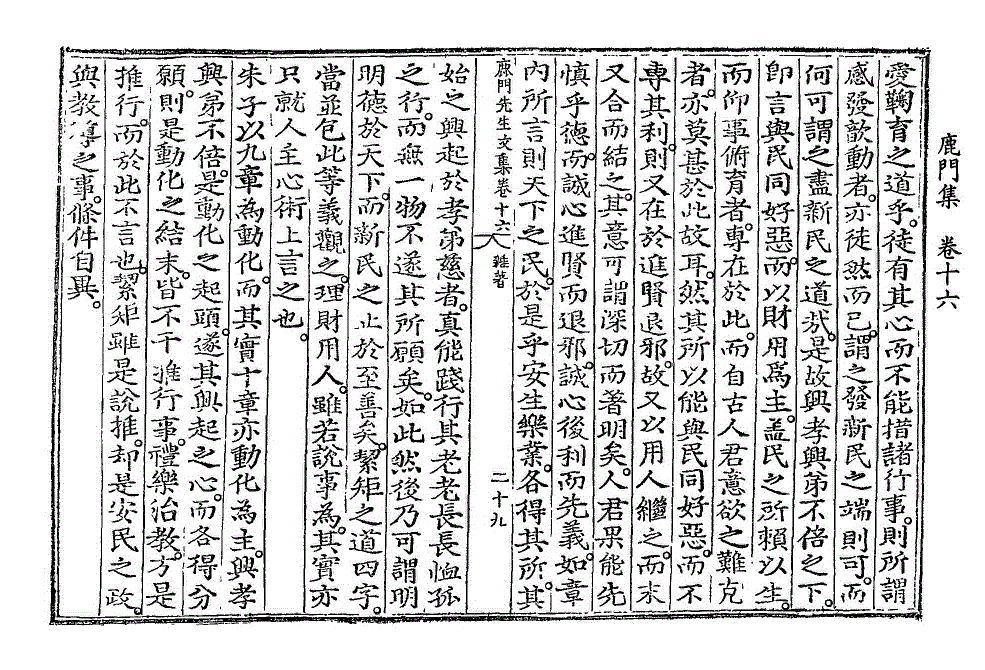 爱鞠育之道乎。徒有其心而不能措诸行事。则所谓感发歆动者。亦徒然而已。谓之发新民之端则可。而何可谓之尽新民之道哉。是故兴孝兴弟不倍之下。即言与民同好恶。而以财用为主。盖民之所赖以生。而仰事俯育者。专在于此。而自古人君意欲之难克者。亦莫甚于此故耳。然其所以能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则又在于进贤退邪。故又以用人继之。而末又合而结之。其意可谓深切而著明矣。人君果能先慎乎德。而诚心进贤而退邪。诚心后利而先义。如章内所言则天下之民。于是乎安生乐业。各得其所。其始之兴起于孝弟慈者。真能践行其老老长长恤孤之行。而无一物不遂其所愿矣。如此然后乃可谓明明德于天下。而新民之止于至善矣。絜矩之道四字。当并包此等义观之。理财用人。虽若说事为。其实亦只就人主心术上言之也。
爱鞠育之道乎。徒有其心而不能措诸行事。则所谓感发歆动者。亦徒然而已。谓之发新民之端则可。而何可谓之尽新民之道哉。是故兴孝兴弟不倍之下。即言与民同好恶。而以财用为主。盖民之所赖以生。而仰事俯育者。专在于此。而自古人君意欲之难克者。亦莫甚于此故耳。然其所以能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则又在于进贤退邪。故又以用人继之。而末又合而结之。其意可谓深切而著明矣。人君果能先慎乎德。而诚心进贤而退邪。诚心后利而先义。如章内所言则天下之民。于是乎安生乐业。各得其所。其始之兴起于孝弟慈者。真能践行其老老长长恤孤之行。而无一物不遂其所愿矣。如此然后乃可谓明明德于天下。而新民之止于至善矣。絜矩之道四字。当并包此等义观之。理财用人。虽若说事为。其实亦只就人主心术上言之也。朱子以九章为动化。而其实十章亦动化为主。兴孝兴弟不倍。是动化之起头。遂其兴起之心。而各得分愿。则是动化之结末。皆不干推行事。礼乐治教。方是推行。而于此不言也。絜矩虽是说推。却是安民之政。与教导之事。条件自异。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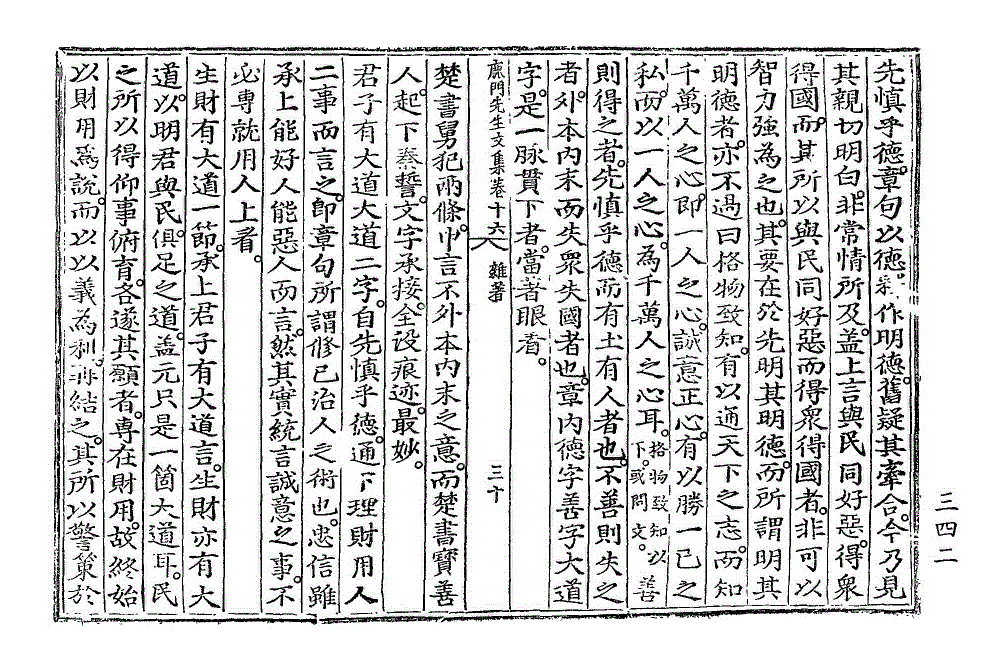 先慎乎德。章句以德释作明德。旧疑其牵合。今乃见其亲切明白。非常情所及。盖上言与民同好恶。得众得国。而其所以与民同好恶而得众得国者。非可以智力强为之也。其要在于先明其明德。而所谓明其明德者。亦不过曰格物致知。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诚意正心。有以胜一己之私。而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耳。(格物致知以下。或问文。)善则得之者。先慎乎德而有土有人者也。不善则失之者。外本内末而失众失国者也。章内德字善字大道字。是一脉贯下者。当著眼看。
先慎乎德。章句以德释作明德。旧疑其牵合。今乃见其亲切明白。非常情所及。盖上言与民同好恶。得众得国。而其所以与民同好恶而得众得国者。非可以智力强为之也。其要在于先明其明德。而所谓明其明德者。亦不过曰格物致知。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诚意正心。有以胜一己之私。而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耳。(格物致知以下。或问文。)善则得之者。先慎乎德而有土有人者也。不善则失之者。外本内末而失众失国者也。章内德字善字大道字。是一脉贯下者。当著眼看。楚书舅犯两条。申言不外本内末之意。而楚书宝善人。起下秦誓。文字承接。全没痕迹。最妙。
君子有大道大道二字。自先慎乎德。通下理财用人二事而言之。即章句所谓修己治人之术也。忠信虽承上能好人能恶人而言。然其实统言诚意之事。不必专就用人上看。
生财有大道一节。承上君子有大道言。生财亦有大道。以明君与民。俱足之道。盖元只是一个大道耳。民之所以得仰事俯育。各遂其愿者。专在财用。故终始以财用为说。而以以义为利。再结之。其所以警策于
鹿门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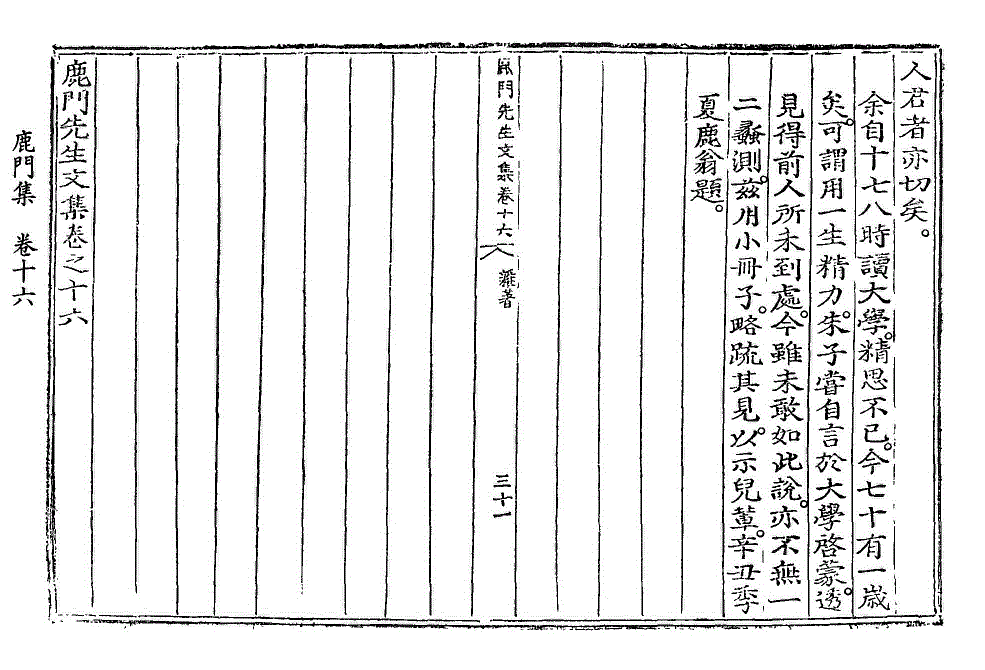 人君者亦切矣。
人君者亦切矣。[附识]
余自十七八时读大学。精思不已。今七十有一岁矣。可谓用一生精力。朱子尝自言于大学,启蒙。透见得前人所未到处。今虽未敢如此说。亦不无一二蠡测。玆用小册子。略疏其见。以示儿辈。辛丑季夏。鹿翁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