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江汉集卷之五 第 x 页
江汉集卷之五
状
状
江汉集卷之五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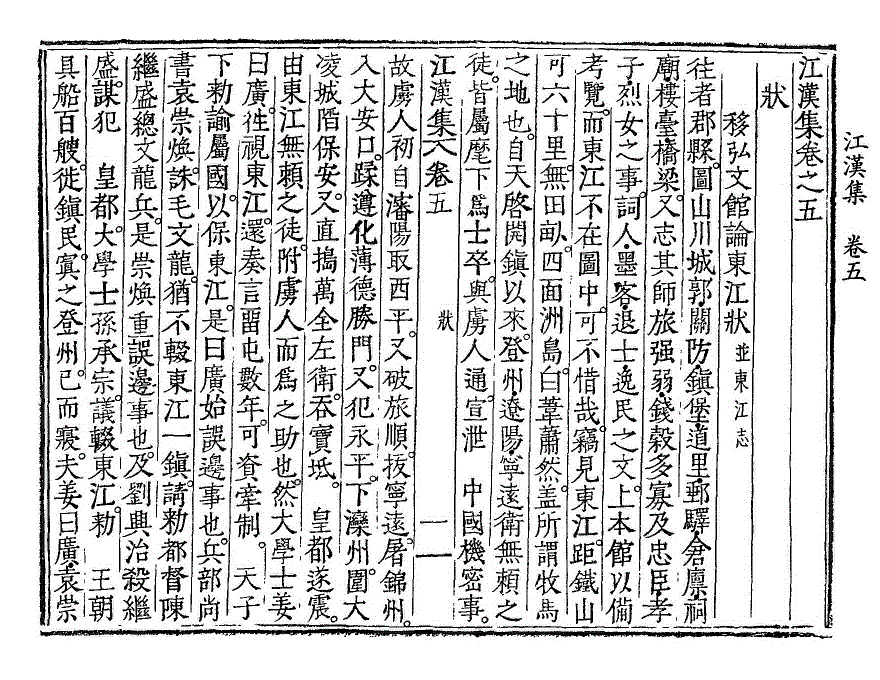 移弘文馆论东江状(并东江志)
移弘文馆论东江状(并东江志)往者郡县。图山川城郭,关防,镇堡,道里,邮驿,仓廪,祠庙,楼台,桥梁。又志其师旅强弱,钱谷多寡及忠臣,孝子,烈女之事。词人,墨客,退士,逸民之文。上本馆以备考览。而东江不在图中。可不惜哉。窃见东江。距铁山可六十里。无田亩。四面洲岛。白苇萧然。盖所谓牧马之地也。自天启开镇以来。登州,辽阳,宁远卫无赖之徒。皆属麾下为士卒。与虏人通。宣泄 中国机密事。故虏人初自沈阳取西平。又破旅顺。拔宁远。屠锦州。入大安口。蹂遵化薄德胜门。又犯永平。下滦州。围大凌城陷保安。又直捣万全左卫。吞宝坻。 皇都遂震。由东江无赖之徒。附虏人而为之助也。然大学士姜曰广。往视东江。还奏言留屯数年。可资牵制。 天子下敕谕属国。以保东江。是曰广始误边事也。兵部尚书袁崇焕。诛毛文龙。犹不辍东江一镇。请敕都督陈继盛总文龙兵。是崇焕重误边事也。及刘兴治杀继盛。谋犯 皇都。大学士孙承宗。议辍东江。敕 王朝具船百艘。徙镇民。寘之登州。已而寝。夫姜曰广,袁崇
江汉集卷之五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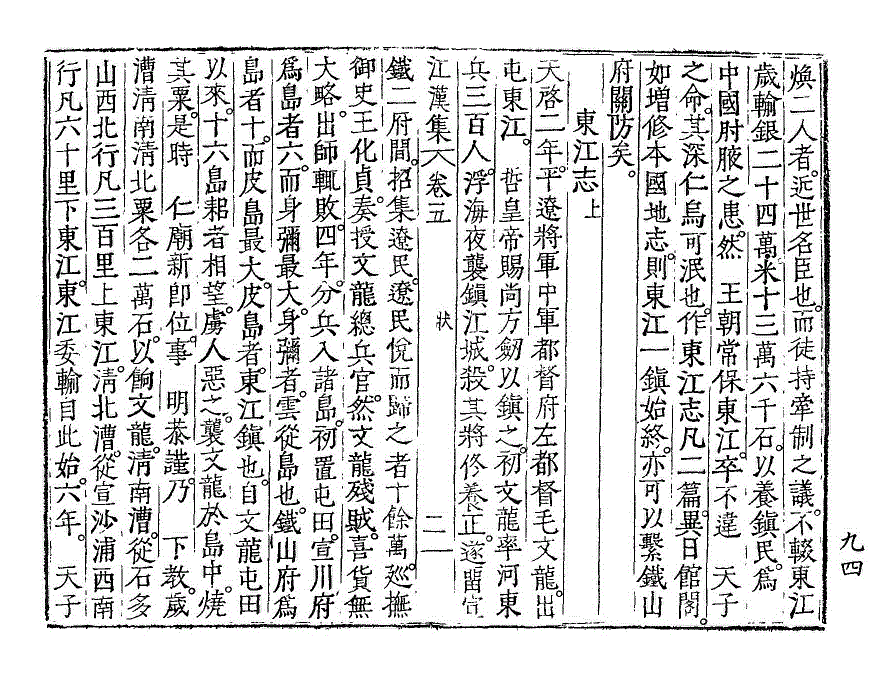 焕二人者。近世名臣也。而徒持牵制之议。不辍东江岁输银二十四万,米十三万六千石。以养镇民。为 中国肘腋之患。然 王朝常保东江。卒不违 天子之命。其深仁乌可泯也。作东江志凡二篇。异日馆阁。如增修本国地志。则东江一镇始终。亦可以系铁山府关防矣。
焕二人者。近世名臣也。而徒持牵制之议。不辍东江岁输银二十四万,米十三万六千石。以养镇民。为 中国肘腋之患。然 王朝常保东江。卒不违 天子之命。其深仁乌可泯也。作东江志凡二篇。异日馆阁。如增修本国地志。则东江一镇始终。亦可以系铁山府关防矣。东江志[上]
天启二年。平辽将军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龙。出屯东江。 哲皇帝赐尚方剑以镇之。初文龙率河东兵三百人。浮海夜袭镇江城。杀其将佟养正。遂留宣铁二府间。招集辽民。辽民悦而归之者十馀万。巡抚御史王化贞。奏授文龙总兵官。然文龙残贼。喜货无大略。出师辄败。四年。分兵入诸岛。初置屯田。宣川府为岛者六。而身弥最大。身弥者。云从岛也。铁山府为岛者十。而皮岛最大。皮岛者。东江镇也。自文龙屯田以来。十六岛耜者相望。虏人恶之。袭文龙于岛中。烧其粟。是时 仁庙新即位。事 明恭谨。乃 下教。岁漕清南清北粟各二万石。以饷文龙。清南漕。从石多山西北行凡三百里上东江。清北漕。从宣沙浦西南行凡六十里下东江。东江委输自此始。六年。 天子
江汉集卷之五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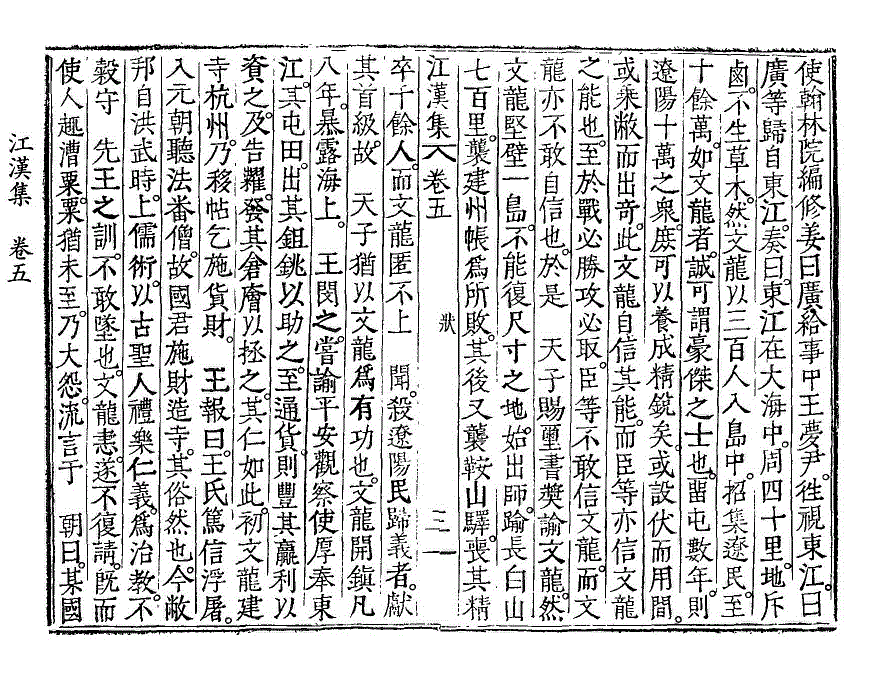 使翰林院编修姜曰广,给事中王梦尹。往视东江。曰广等归自东江。奏曰。东江在大海中。周四十里。地斥卤。不生草木。然文龙以三百人入岛中。招集辽民。至十馀万。如文龙者。诚可谓豪杰之士也。留屯数年。则辽阳十万之众。庶可以养成精锐矣。或设伏而用间。或乘敝而出奇。此文龙自信其能。而臣等亦信文龙之能也。至于战必胜攻必取。臣等不敢信文龙。而文龙亦不敢自信也。于是 天子赐玺书奖谕文龙。然文龙坚壁一岛。不能复尺寸之地。始出师。踰长白山七百里。袭建州帐为所败。其后又袭鞍山驿。丧其精卒千馀人。而文龙匿不上 闻。杀辽阳民归义者。献其首级。故 天子犹以文龙为有功也。文龙开镇凡八年。暴露海上。 王闵之。尝谕平安观察使厚奉东江。其屯田。出其锄铫以助之。至通货。则丰其赢利以资之。及告粜。发其仓廥以拯之。其仁如此。初文龙建寺杭州。乃移帖乞施货财。 王报曰。王氏笃信浮屠。入元朝听法番僧。故国君施财造寺。其俗然也。今敝邦自洪武时。上儒术。以古圣人礼乐仁义。为治教。不谷守 先王之训。不敢坠也。文龙恚。遂不复请。既而使人趣漕粟。粟犹未至。乃大怨。流言于 朝曰。某国
使翰林院编修姜曰广,给事中王梦尹。往视东江。曰广等归自东江。奏曰。东江在大海中。周四十里。地斥卤。不生草木。然文龙以三百人入岛中。招集辽民。至十馀万。如文龙者。诚可谓豪杰之士也。留屯数年。则辽阳十万之众。庶可以养成精锐矣。或设伏而用间。或乘敝而出奇。此文龙自信其能。而臣等亦信文龙之能也。至于战必胜攻必取。臣等不敢信文龙。而文龙亦不敢自信也。于是 天子赐玺书奖谕文龙。然文龙坚壁一岛。不能复尺寸之地。始出师。踰长白山七百里。袭建州帐为所败。其后又袭鞍山驿。丧其精卒千馀人。而文龙匿不上 闻。杀辽阳民归义者。献其首级。故 天子犹以文龙为有功也。文龙开镇凡八年。暴露海上。 王闵之。尝谕平安观察使厚奉东江。其屯田。出其锄铫以助之。至通货。则丰其赢利以资之。及告粜。发其仓廥以拯之。其仁如此。初文龙建寺杭州。乃移帖乞施货财。 王报曰。王氏笃信浮屠。入元朝听法番僧。故国君施财造寺。其俗然也。今敝邦自洪武时。上儒术。以古圣人礼乐仁义。为治教。不谷守 先王之训。不敢坠也。文龙恚。遂不复请。既而使人趣漕粟。粟犹未至。乃大怨。流言于 朝曰。某国江汉集卷之五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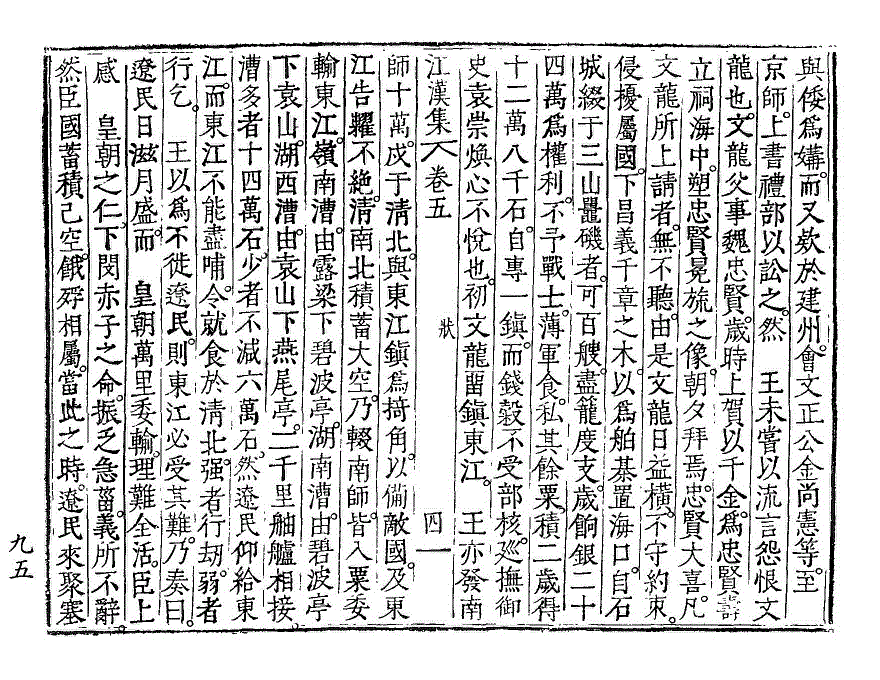 与倭为媾。而又款于建州。会文正公金尚宪等。至 京师。上书礼部以讼之。然 王未尝以流言怨恨文龙也。文龙父事魏忠贤。岁时上贺以千金。为忠贤寿立祠海中。塑忠贤冕旒之像。朝夕拜焉。忠贤大喜。凡文龙所上请者。无不听。由是文龙日益横。不守约束。侵扰属国。下昌义千章之木。以为舶棋置海口。自石城缀于三山鼍矶者。可百艘。尽笼度支。岁饷银二十四万为权利。不予战士。薄军食。私其馀粟。积二岁得十二万八千石。自专一镇。而钱谷不受部核。巡抚御史袁崇焕心不悦也。初文龙留镇东江。 王亦发南师十万。戍于清北。与东江镇为掎角。以备敌国。及东江告粜不绝。清南北积蓄大空。乃辍南师。皆入粟委输东江。岭南漕。由露梁下碧波亭。湖南漕。由碧波亭下袁山。湖西漕。由袁山下燕尾亭。二千里舳舻相接。漕多者十四万石。少者不减六万石。然辽民仰给东江。而东江不能尽哺。令就食于清北。强者行劫。弱者行乞。 王以为不徙辽民。则东江必受其难。乃奏曰。辽民日滋月盛。而 皇朝万里委输。理难全活。臣上感 皇朝之仁。下闵赤子之命。振乏急菑。义所不辞。然臣国蓄积已空。饿殍相属。当此之时。辽民来聚塞
与倭为媾。而又款于建州。会文正公金尚宪等。至 京师。上书礼部以讼之。然 王未尝以流言怨恨文龙也。文龙父事魏忠贤。岁时上贺以千金。为忠贤寿立祠海中。塑忠贤冕旒之像。朝夕拜焉。忠贤大喜。凡文龙所上请者。无不听。由是文龙日益横。不守约束。侵扰属国。下昌义千章之木。以为舶棋置海口。自石城缀于三山鼍矶者。可百艘。尽笼度支。岁饷银二十四万为权利。不予战士。薄军食。私其馀粟。积二岁得十二万八千石。自专一镇。而钱谷不受部核。巡抚御史袁崇焕心不悦也。初文龙留镇东江。 王亦发南师十万。戍于清北。与东江镇为掎角。以备敌国。及东江告粜不绝。清南北积蓄大空。乃辍南师。皆入粟委输东江。岭南漕。由露梁下碧波亭。湖南漕。由碧波亭下袁山。湖西漕。由袁山下燕尾亭。二千里舳舻相接。漕多者十四万石。少者不减六万石。然辽民仰给东江。而东江不能尽哺。令就食于清北。强者行劫。弱者行乞。 王以为不徙辽民。则东江必受其难。乃奏曰。辽民日滋月盛。而 皇朝万里委输。理难全活。臣上感 皇朝之仁。下闵赤子之命。振乏急菑。义所不辞。然臣国蓄积已空。饿殍相属。当此之时。辽民来聚塞江汉集卷之五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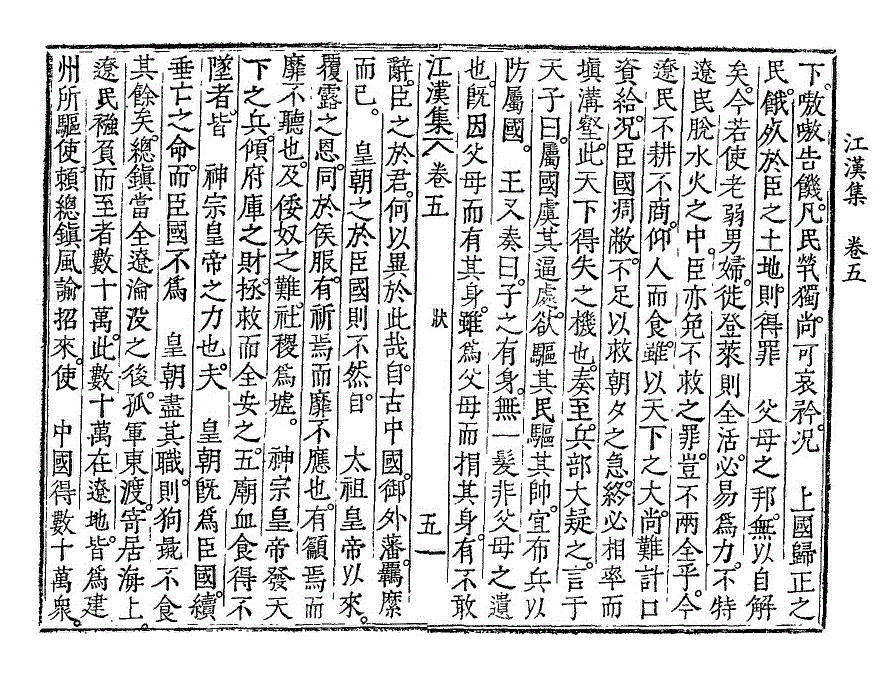 下。嗷嗷告饥。凡民煢独。尚可哀矜。况 上国归正之民。饿死于臣之土地。则得罪 父母之邦。无以自解矣。今若使老弱男妇。徙登莱则全活。必易为力。不特辽民脱水火之中。臣亦免不救之罪。岂不两全乎。今辽民不耕不商。仰人而食。虽以天下之大。尚难计口资给。况臣国凋敝。不足以救朝夕之急。终必相率而填沟壑。此天下得失之机也。奏至。兵部大疑之。言于天子曰。属国虞其逼处。欲驱其民驱其帅。宜布兵以防属国。 王又奏曰。子之有身。无一发非父母之遗也。既因父母而有其身。虽为父母而捐其身。有不敢辞。臣之于君。何以异于此哉。自古中国。御外藩。羁縻而已。 皇朝之于臣国则不然。自 太祖皇帝以来。覆露之恩。同于侯服。有祈焉而靡不应也。有吁焉而靡不听也。及倭奴之难。社稷为墟。 神宗皇帝发天下之兵。倾府库之财。拯救而全安之。五庙血食得不坠者。皆 神宗皇帝之力也。夫 皇朝既为臣国。续垂亡之命。而臣国不为 皇朝尽其职。则狗彘不食其馀矣。总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居海上。辽民襁负而至者数十万。此数十万在辽地。皆为建州所驱使。赖总镇风谕招来。使 中国得数十万众。
下。嗷嗷告饥。凡民煢独。尚可哀矜。况 上国归正之民。饿死于臣之土地。则得罪 父母之邦。无以自解矣。今若使老弱男妇。徙登莱则全活。必易为力。不特辽民脱水火之中。臣亦免不救之罪。岂不两全乎。今辽民不耕不商。仰人而食。虽以天下之大。尚难计口资给。况臣国凋敝。不足以救朝夕之急。终必相率而填沟壑。此天下得失之机也。奏至。兵部大疑之。言于天子曰。属国虞其逼处。欲驱其民驱其帅。宜布兵以防属国。 王又奏曰。子之有身。无一发非父母之遗也。既因父母而有其身。虽为父母而捐其身。有不敢辞。臣之于君。何以异于此哉。自古中国。御外藩。羁縻而已。 皇朝之于臣国则不然。自 太祖皇帝以来。覆露之恩。同于侯服。有祈焉而靡不应也。有吁焉而靡不听也。及倭奴之难。社稷为墟。 神宗皇帝发天下之兵。倾府库之财。拯救而全安之。五庙血食得不坠者。皆 神宗皇帝之力也。夫 皇朝既为臣国。续垂亡之命。而臣国不为 皇朝尽其职。则狗彘不食其馀矣。总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居海上。辽民襁负而至者数十万。此数十万在辽地。皆为建州所驱使。赖总镇风谕招来。使 中国得数十万众。江汉集卷之五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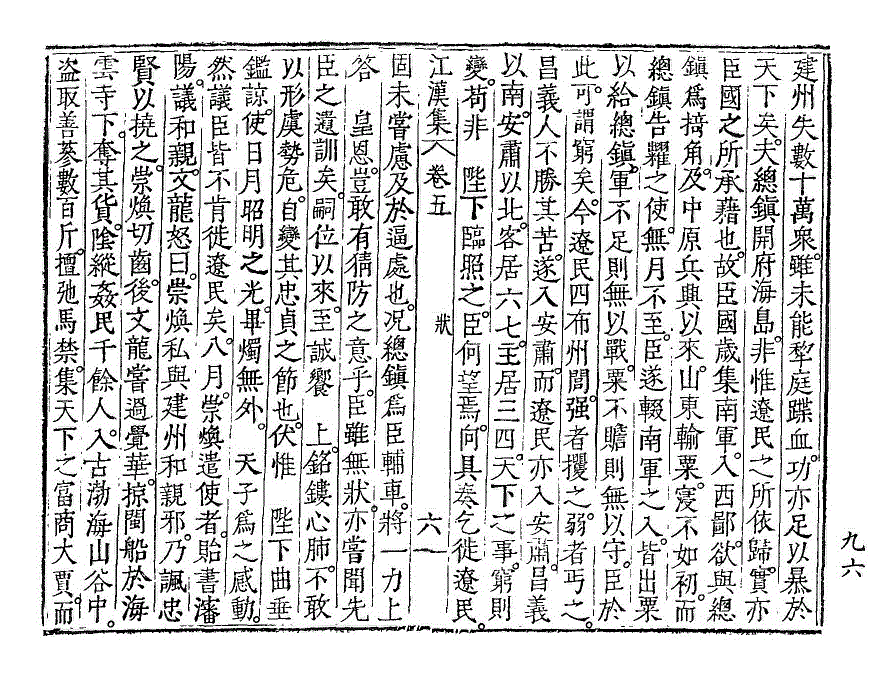 建州失数十万众。虽未能犁庭蹀血。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夫总镇开府海岛。非惟辽民之所依归。实亦臣国之所承藉也。故臣国岁集南军。入西鄙。欲与总镇为掎角。及中原兵兴以来。山东输粟。寖不如初。而总镇告粜之使。无月不至。臣遂辍南军之入。皆出粟以给总镇。军不足则无以战。粟不赡则无以守。臣于此。可谓穷矣。今辽民四布州闾。强者攫之。弱者丐之。昌义人不胜其苦。遂入安肃。而辽民亦入安肃。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天下之事。穷则变。苟非 陛下临照之。臣何望焉。向具奏乞徙辽民。固未尝虑及于逼处也。况总镇为臣辅车。将一力上答 皇恩。岂敢有猜防之意乎。臣虽无状。亦尝闻先臣之遗训矣。嗣位以来。至诚飨 上。铭镂心肺。不敢以形虞势危。自变其忠贞之节也。伏惟 陛下曲垂鉴谅。使日月昭明之光。毕烛无外。 天子为之感动。然议臣皆不肯徙辽民矣。八月。崇焕遣使者。贻书沈阳。议和亲。文龙怒曰。崇焕私与建州和亲邪。乃讽忠贤以挠之。崇焕切齿。后文龙尝过觉华。掠闽船于海云寺下。夺其货。阴纵奸民千馀人。入古渤海山谷中。盗取善蔘数百斤。擅弛马禁。集天下之富商大贾。而
建州失数十万众。虽未能犁庭蹀血。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夫总镇开府海岛。非惟辽民之所依归。实亦臣国之所承藉也。故臣国岁集南军。入西鄙。欲与总镇为掎角。及中原兵兴以来。山东输粟。寖不如初。而总镇告粜之使。无月不至。臣遂辍南军之入。皆出粟以给总镇。军不足则无以战。粟不赡则无以守。臣于此。可谓穷矣。今辽民四布州闾。强者攫之。弱者丐之。昌义人不胜其苦。遂入安肃。而辽民亦入安肃。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天下之事。穷则变。苟非 陛下临照之。臣何望焉。向具奏乞徙辽民。固未尝虑及于逼处也。况总镇为臣辅车。将一力上答 皇恩。岂敢有猜防之意乎。臣虽无状。亦尝闻先臣之遗训矣。嗣位以来。至诚飨 上。铭镂心肺。不敢以形虞势危。自变其忠贞之节也。伏惟 陛下曲垂鉴谅。使日月昭明之光。毕烛无外。 天子为之感动。然议臣皆不肯徙辽民矣。八月。崇焕遣使者。贻书沈阳。议和亲。文龙怒曰。崇焕私与建州和亲邪。乃讽忠贤以挠之。崇焕切齿。后文龙尝过觉华。掠闽船于海云寺下。夺其货。阴纵奸民千馀人。入古渤海山谷中。盗取善蔘数百斤。擅弛马禁。集天下之富商大贾。而江汉集卷之五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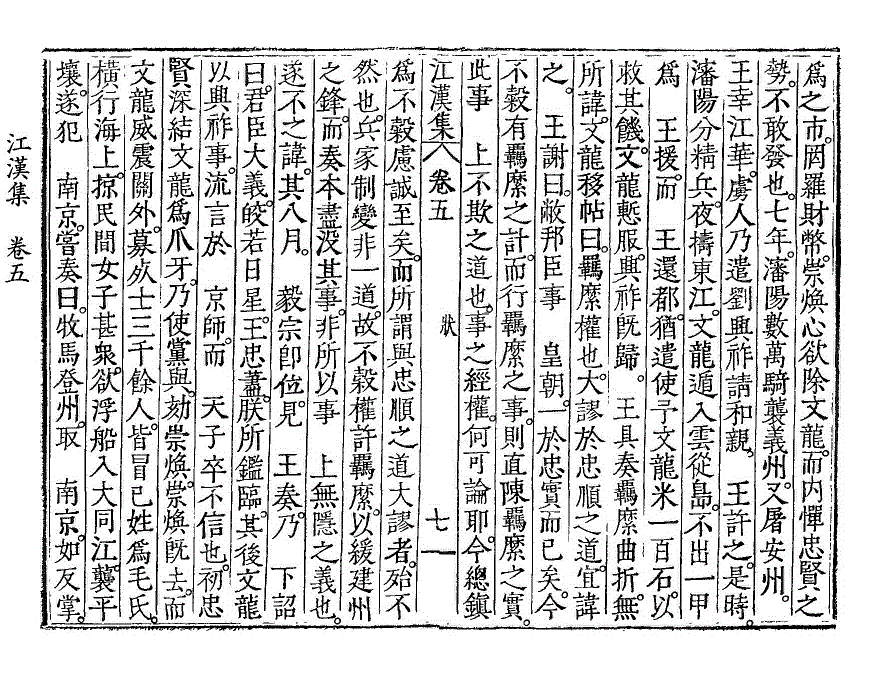 为之市。罔罗财币。崇焕心欲除文龙。而内惮忠贤之势。不敢发也。七年。沈阳数万骑袭义州。又屠安州。 王幸江华。虏人乃遣刘兴祚请和亲。 王许之。是时。沈阳分精兵。夜捣东江。文龙遁入云从岛。不出一甲为 王援。而 王还都。犹遣使予文龙米一百石。以救其饥。文龙惭服。兴祚既归。 王具奏羁縻曲折。无所讳。文龙移帖曰。羁縻权也。大谬于忠顺之道。宜讳之。 王谢曰。敝邦臣事 皇朝。一于忠实而已矣。今不谷有羁縻之计。而行羁縻之事。则直陈羁縻之实。此事 上不欺之道也。事之经权。何可论耶。今总镇为不谷虑诚至矣。而所谓与忠顺之道大谬者。殆不然也。兵家制变非一道。故不谷权许羁縻。以缓建州之锋。而奏本尽没其事。非所以事 上无隐之义也。遂不之讳。其八月。 毅宗即位。见 王奏。乃 下诏曰。君臣大义。皎若日星。王忠荩。朕所鉴临。其后文龙以兴祚事。流言于 京师。而 天子卒不信也。初忠贤深结文龙为爪牙。乃使党与。劾崇焕。崇焕既去。而文龙威震关外。募死士三千馀人。皆冒己姓为毛氏。横行海上。掠民间女子甚众。欲浮船入大同江。袭平壤。遂犯 南京。尝奏曰。牧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
为之市。罔罗财币。崇焕心欲除文龙。而内惮忠贤之势。不敢发也。七年。沈阳数万骑袭义州。又屠安州。 王幸江华。虏人乃遣刘兴祚请和亲。 王许之。是时。沈阳分精兵。夜捣东江。文龙遁入云从岛。不出一甲为 王援。而 王还都。犹遣使予文龙米一百石。以救其饥。文龙惭服。兴祚既归。 王具奏羁縻曲折。无所讳。文龙移帖曰。羁縻权也。大谬于忠顺之道。宜讳之。 王谢曰。敝邦臣事 皇朝。一于忠实而已矣。今不谷有羁縻之计。而行羁縻之事。则直陈羁縻之实。此事 上不欺之道也。事之经权。何可论耶。今总镇为不谷虑诚至矣。而所谓与忠顺之道大谬者。殆不然也。兵家制变非一道。故不谷权许羁縻。以缓建州之锋。而奏本尽没其事。非所以事 上无隐之义也。遂不之讳。其八月。 毅宗即位。见 王奏。乃 下诏曰。君臣大义。皎若日星。王忠荩。朕所鉴临。其后文龙以兴祚事。流言于 京师。而 天子卒不信也。初忠贤深结文龙为爪牙。乃使党与。劾崇焕。崇焕既去。而文龙威震关外。募死士三千馀人。皆冒己姓为毛氏。横行海上。掠民间女子甚众。欲浮船入大同江。袭平壤。遂犯 南京。尝奏曰。牧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江汉集卷之五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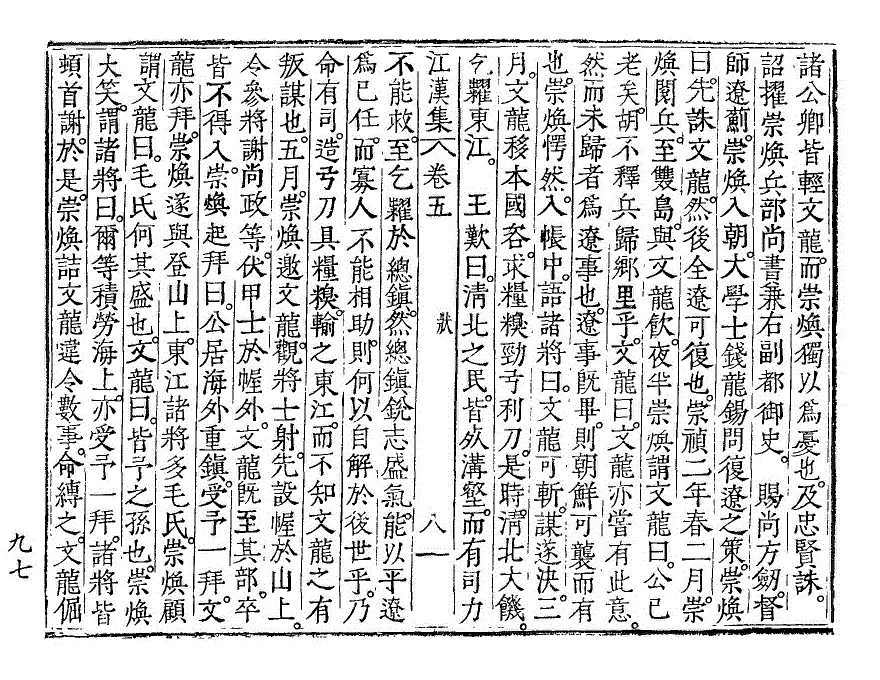 诸公卿皆轻文龙。而崇焕独以为忧也。及忠贤诛。 诏擢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赐尚方剑。督师辽蓟。崇焕入朝。大学士钱龙锡问复辽之策。崇焕曰。先诛文龙。然后全辽可复也。崇祯二年春二月。崇焕阅兵。至双岛。与文龙饮。夜半崇焕谓文龙曰。公已老矣。胡不释兵归乡里乎。文龙曰。文龙亦尝有此意。然而未归者为辽事也。辽事既毕。则朝鲜可袭而有也。崇焕愕然。入帐中。语诸将曰。文龙可斩。谋遂决。三月。文龙移本国咨。求粮糗劲弓利刀。是时。清北大饥。乞粜东江。 王叹曰。清北之民。皆死沟壑。而有司力不能救。至乞粜于总镇。然总镇锐志盛气。能以平辽为己任。而寡人不能相助。则何以自解于后世乎。乃命有司。造弓刀具粮糗。输之东江。而不知文龙之有叛谋也。五月。崇焕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于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于幄外。文龙既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焕起拜曰。公居海外重镇。受予一拜。文龙亦拜。崇焕遂与登山上。东江诸将多毛氏。崇焕顾谓文龙曰。毛氏何其盛也。文龙曰。皆予之孙也。崇焕大笑。谓诸将曰。尔等积劳海上。亦受予一拜。诸将皆顿首谢。于是。崇焕诘文龙违令数事。命缚之。文龙倔
诸公卿皆轻文龙。而崇焕独以为忧也。及忠贤诛。 诏擢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赐尚方剑。督师辽蓟。崇焕入朝。大学士钱龙锡问复辽之策。崇焕曰。先诛文龙。然后全辽可复也。崇祯二年春二月。崇焕阅兵。至双岛。与文龙饮。夜半崇焕谓文龙曰。公已老矣。胡不释兵归乡里乎。文龙曰。文龙亦尝有此意。然而未归者为辽事也。辽事既毕。则朝鲜可袭而有也。崇焕愕然。入帐中。语诸将曰。文龙可斩。谋遂决。三月。文龙移本国咨。求粮糗劲弓利刀。是时。清北大饥。乞粜东江。 王叹曰。清北之民。皆死沟壑。而有司力不能救。至乞粜于总镇。然总镇锐志盛气。能以平辽为己任。而寡人不能相助。则何以自解于后世乎。乃命有司。造弓刀具粮糗。输之东江。而不知文龙之有叛谋也。五月。崇焕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于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于幄外。文龙既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焕起拜曰。公居海外重镇。受予一拜。文龙亦拜。崇焕遂与登山上。东江诸将多毛氏。崇焕顾谓文龙曰。毛氏何其盛也。文龙曰。皆予之孙也。崇焕大笑。谓诸将曰。尔等积劳海上。亦受予一拜。诸将皆顿首谢。于是。崇焕诘文龙违令数事。命缚之。文龙倔江汉集卷之五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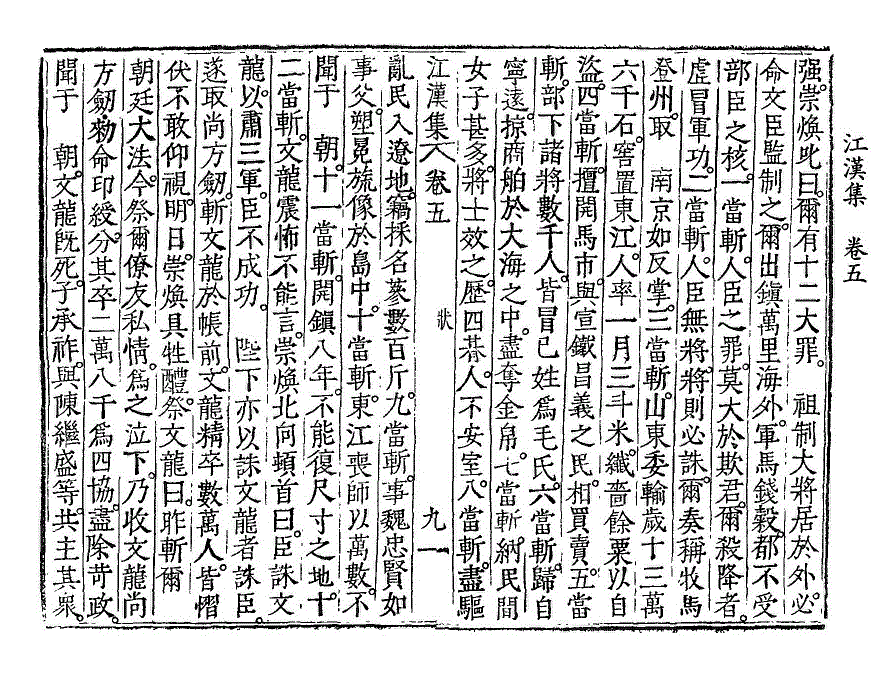 强。崇焕叱曰。尔有十二大罪。 祖制大将居于外。必命文臣监制之。尔出镇万里海外。军马钱谷。都不受部臣之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尔杀降者。虚冒军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三当斩。山东委输岁十三万六千石。窖置东江。人率一月三斗米。纤啬馀粟以自盗。四当斩。擅开马市。与宣铁昌义之民。相买卖。五当斩。部下诸将数千人。皆冒己姓为毛氏。六当斩。归自宁远。掠商舶于大海之中。尽夺金帛。七当斩。纳民间女子甚多。将士效之。历四期。人不安室。八当斩。尽驱乱民入辽地。窃采名蔘数百斤。九当斩。事魏忠贤如事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东江丧师以万数。不闻于 朝。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地。十二当斩。文龙震怖不能言。崇焕北向顿首曰。臣诛文龙。以肃三军。臣不成功。 陛下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文龙于帐前。文龙精卒数万人。皆慑伏不敢仰视。明日。崇焕具牲醴。祭文龙曰。昨斩尔 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之泣下。乃收文龙尚方剑,敕命印绶。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尽除苛政。闻于 朝。文龙既死。子承祚。与陈继盛等。共主其众。
强。崇焕叱曰。尔有十二大罪。 祖制大将居于外。必命文臣监制之。尔出镇万里海外。军马钱谷。都不受部臣之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尔杀降者。虚冒军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 南京如反掌。三当斩。山东委输岁十三万六千石。窖置东江。人率一月三斗米。纤啬馀粟以自盗。四当斩。擅开马市。与宣铁昌义之民。相买卖。五当斩。部下诸将数千人。皆冒己姓为毛氏。六当斩。归自宁远。掠商舶于大海之中。尽夺金帛。七当斩。纳民间女子甚多。将士效之。历四期。人不安室。八当斩。尽驱乱民入辽地。窃采名蔘数百斤。九当斩。事魏忠贤如事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东江丧师以万数。不闻于 朝。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地。十二当斩。文龙震怖不能言。崇焕北向顿首曰。臣诛文龙。以肃三军。臣不成功。 陛下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文龙于帐前。文龙精卒数万人。皆慑伏不敢仰视。明日。崇焕具牲醴。祭文龙曰。昨斩尔 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之泣下。乃收文龙尚方剑,敕命印绶。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尽除苛政。闻于 朝。文龙既死。子承祚。与陈继盛等。共主其众。江汉集卷之五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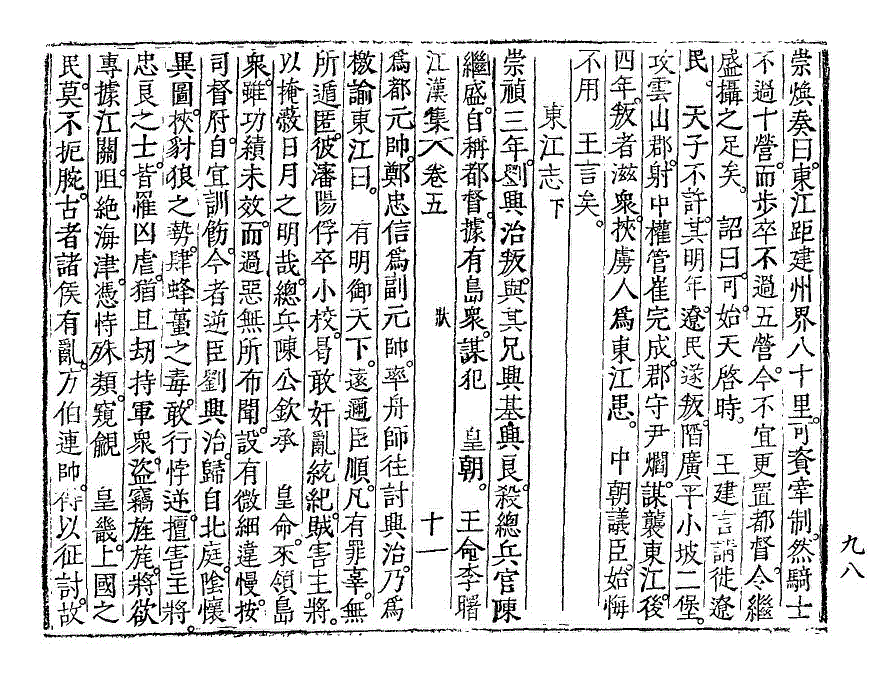 崇焕奏曰。东江距建州界八十里。可资牵制。然骑士不过十营。而步卒不过五营。今不宜更置都督。令继盛摄之足矣。 诏曰。可。始天启时。 王建言请徙辽民。 天子不许。其明年。辽民遂叛。陷广平小坡二堡。攻云山郡。射中权管崔完成。郡守尹爓。谋袭东江。后四年。叛者滋众。挟虏人为东江患。 中朝议臣。始悔不用 王言矣。
崇焕奏曰。东江距建州界八十里。可资牵制。然骑士不过十营。而步卒不过五营。今不宜更置都督。令继盛摄之足矣。 诏曰。可。始天启时。 王建言请徙辽民。 天子不许。其明年。辽民遂叛。陷广平小坡二堡。攻云山郡。射中权管崔完成。郡守尹爓。谋袭东江。后四年。叛者滋众。挟虏人为东江患。 中朝议臣。始悔不用 王言矣。东江志[下]
崇祯三年。刘兴治叛。与其兄兴基,兴良。杀总兵官陈继盛。自称都督。据有岛众。谋犯 皇朝。 王命李曙为都元帅。郑忠信为副元帅。率舟师往讨兴治。乃为檄谕东江曰。 有明御天下。远迩臣顺。凡有罪辜。无所遁匿。彼沈阳俘卒小校。曷敢奸乱统纪。贼害主将。以掩蔽日月之明哉。总兵陈公钦承 皇命。来领岛众。虽功绩未效。而过恶无所布闻。设有微细违慢。按司督府。自宜训饬。今者逆臣刘兴治。归自北庭。阴怀异图。挟豺狼之势。肆蜂虿之毒。敢行悖逆。擅害主将。忠良之士。皆罹凶虐。犹且劫持军众。盗窃旌旄。将欲专据江关。阻绝海津。凭恃殊类。窥觎 皇畿。上国之民。莫不扼腕。古者诸侯有乱。方伯连帅。得以征讨。故
江汉集卷之五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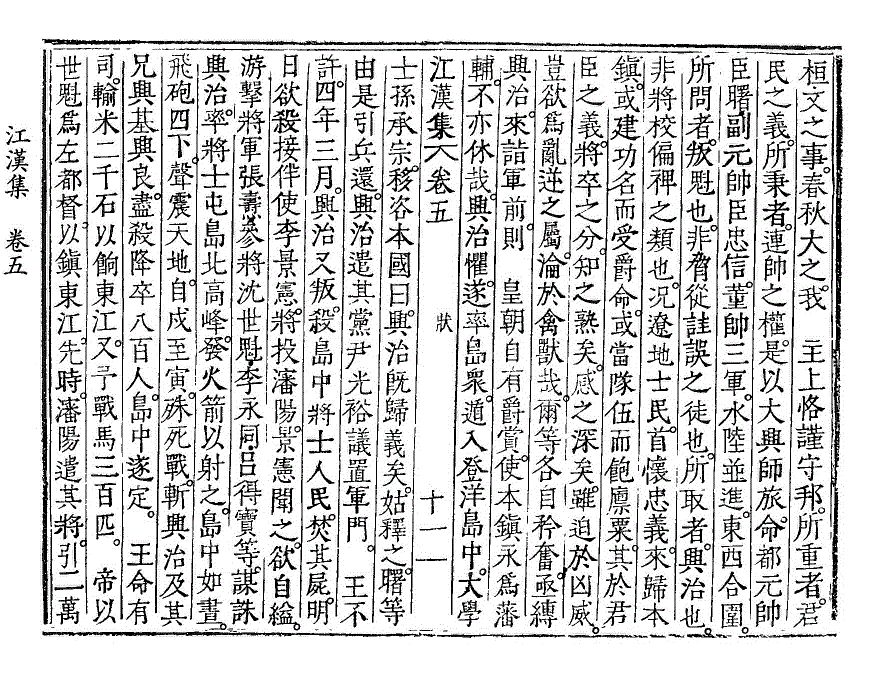 桓文之事。春秋大之。我 主上恪谨守邦。所重者。君民之义。所秉者。连帅之权。是以大兴师旅。命都元帅臣曙,副元帅臣忠信。董帅三军。水陆并进。东西合围。所问者。叛魁也。非胁从诖误之徒也。所取者。兴治也。非将校偏裨之类也。况辽地士民。首怀忠义。来归本镇。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当队伍而饱廪粟。其于君臣之义。将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虽迫于凶威。岂欲为乱逆之属。沦于禽兽哉。尔等各自矜奋。亟缚兴治。来诣军前。则 皇朝自有爵赏。使本镇永为藩辅。不亦休哉。兴治惧。遂率岛众。遁入登洋岛中。大学士孙承宗。移咨本国曰。兴治既归义矣。姑释之。曙等由是引兵还。兴治遣其党尹光裕议置军门。 王不许。四年三月。兴治又叛。杀岛中将士人民。焚其尸。明日欲杀接伴使李景宪。将投沈阳。景宪闻之。欲自缢。游击将军张焘,参将沈世魁,李永同,吕得宝等。谋诛兴治。率将士屯岛北高峰。发火箭以射之。岛中如昼。飞炮四下。声震天地。自戌至寅。殊死战。斩兴治及其兄兴基,兴良。尽杀降卒八百人。岛中遂定。 王命有司。输米二千石以饷东江。又予战马三百匹。 帝以世魁为左都督。以镇东江。先时。沈阳遣其将。引二万
桓文之事。春秋大之。我 主上恪谨守邦。所重者。君民之义。所秉者。连帅之权。是以大兴师旅。命都元帅臣曙,副元帅臣忠信。董帅三军。水陆并进。东西合围。所问者。叛魁也。非胁从诖误之徒也。所取者。兴治也。非将校偏裨之类也。况辽地士民。首怀忠义。来归本镇。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当队伍而饱廪粟。其于君臣之义。将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虽迫于凶威。岂欲为乱逆之属。沦于禽兽哉。尔等各自矜奋。亟缚兴治。来诣军前。则 皇朝自有爵赏。使本镇永为藩辅。不亦休哉。兴治惧。遂率岛众。遁入登洋岛中。大学士孙承宗。移咨本国曰。兴治既归义矣。姑释之。曙等由是引兵还。兴治遣其党尹光裕议置军门。 王不许。四年三月。兴治又叛。杀岛中将士人民。焚其尸。明日欲杀接伴使李景宪。将投沈阳。景宪闻之。欲自缢。游击将军张焘,参将沈世魁,李永同,吕得宝等。谋诛兴治。率将士屯岛北高峰。发火箭以射之。岛中如昼。飞炮四下。声震天地。自戌至寅。殊死战。斩兴治及其兄兴基,兴良。尽杀降卒八百人。岛中遂定。 王命有司。输米二千石以饷东江。又予战马三百匹。 帝以世魁为左都督。以镇东江。先时。沈阳遣其将。引二万江汉集卷之五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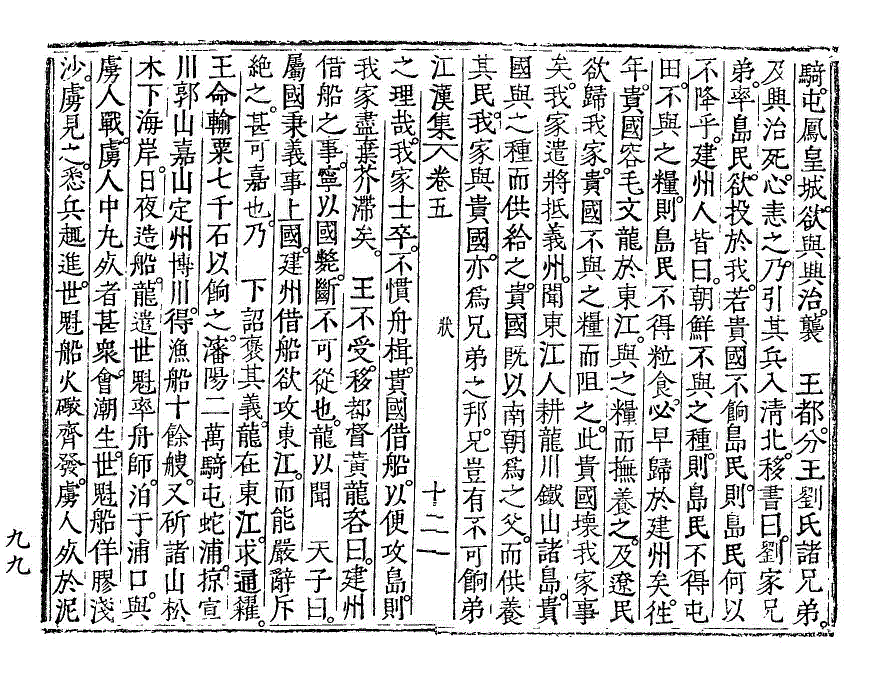 骑。屯凤皇城。欲与兴治。袭 王都。分王刘氏诸兄弟。及兴治死。心恚之。乃引其兵入清北。移书曰。刘家兄弟。率岛民。欲投于我。若贵国不饷岛民。则岛民何以不降乎。建州人皆曰。朝鲜不与之种。则岛民不得屯田。不与之粮。则岛民不得粒食。必早归于建州矣。往年。贵国容毛文龙于东江。与之粮而抚养之。及辽民欲归我家。贵国不与之粮而阻之。此贵国坏我家事矣。我家遣将抵义州。闻东江人耕龙川铁山诸岛。贵国与之种而供给之。贵国既以南朝为之父。而供养其民。我家与贵国。亦为兄弟之邦。兄岂有不可饷弟之理哉。我家士卒。不惯舟楫。贵国借船。以便攻岛。则我家尽弃芥滞矣。 王不受。移都督黄龙咨曰。建州借船之事。宁以国毙。断不可从也。龙以闻 天子曰。属国秉义事上国。建州借船欲攻东江。而能严辞斥绝之。甚可嘉也。乃 下诏褒其义。龙在东江。求通籴。王命输粟七千石以饷之。沈阳二万骑屯蛇浦。掠宣川郭山嘉山定州博川。得渔船十馀艘。又斫诸山松木下海岸。日夜造船。龙遣世魁率舟师。泊于浦口。与虏人战。虏人中丸死者甚众。会潮生。世魁船佯胶浅沙。虏见之。悉兵趣进。世魁船火炮齐发。虏人死于泥
骑。屯凤皇城。欲与兴治。袭 王都。分王刘氏诸兄弟。及兴治死。心恚之。乃引其兵入清北。移书曰。刘家兄弟。率岛民。欲投于我。若贵国不饷岛民。则岛民何以不降乎。建州人皆曰。朝鲜不与之种。则岛民不得屯田。不与之粮。则岛民不得粒食。必早归于建州矣。往年。贵国容毛文龙于东江。与之粮而抚养之。及辽民欲归我家。贵国不与之粮而阻之。此贵国坏我家事矣。我家遣将抵义州。闻东江人耕龙川铁山诸岛。贵国与之种而供给之。贵国既以南朝为之父。而供养其民。我家与贵国。亦为兄弟之邦。兄岂有不可饷弟之理哉。我家士卒。不惯舟楫。贵国借船。以便攻岛。则我家尽弃芥滞矣。 王不受。移都督黄龙咨曰。建州借船之事。宁以国毙。断不可从也。龙以闻 天子曰。属国秉义事上国。建州借船欲攻东江。而能严辞斥绝之。甚可嘉也。乃 下诏褒其义。龙在东江。求通籴。王命输粟七千石以饷之。沈阳二万骑屯蛇浦。掠宣川郭山嘉山定州博川。得渔船十馀艘。又斫诸山松木下海岸。日夜造船。龙遣世魁率舟师。泊于浦口。与虏人战。虏人中丸死者甚众。会潮生。世魁船佯胶浅沙。虏见之。悉兵趣进。世魁船火炮齐发。虏人死于泥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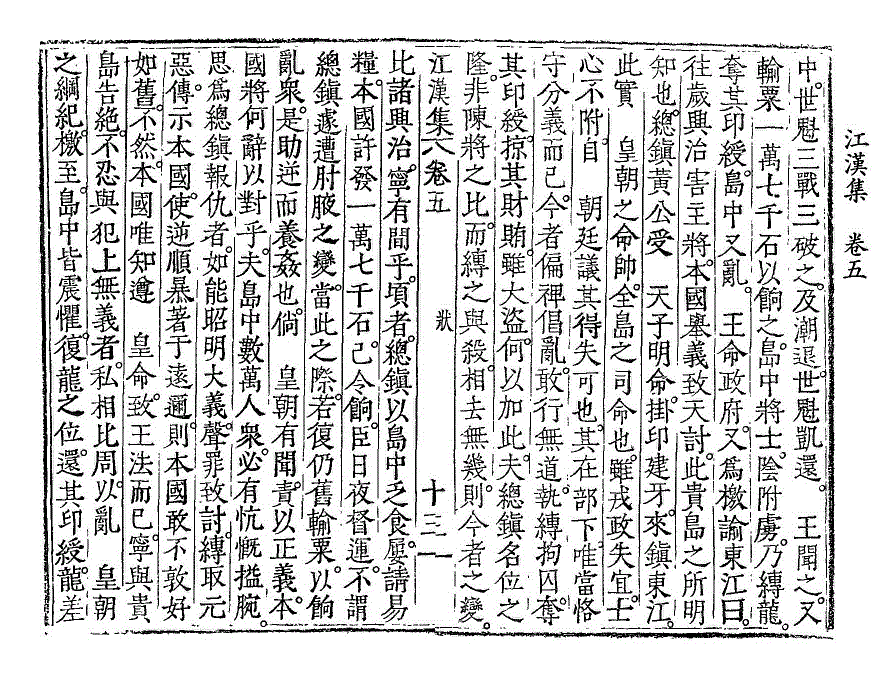 中。世魁三战三破之。及潮退。世魁凯还。 王闻之。又输粟一万七千石以饷之。岛中将士。阴附虏。乃缚龙。夺其印绶。岛中又乱。 王命政府。又为檄谕东江曰。往岁兴治害主将。本国举义致天讨。此贵岛之所明知也。总镇黄公受 天子明命。挂印建牙。来镇东江。此实 皇朝之命帅。全岛之司命也。虽戎政失宜。士心不附。自 朝廷议其得失可也。其在部下。唯当恪守分义而已。今者偏裨倡乱。敢行无道。执缚拘囚。夺其印绶。掠其财贿。虽大盗。何以加此。夫总镇名位之隆。非陈将之比。而缚之与杀。相去无几。则今者之变。比诸兴治。宁有间乎。顷者。总镇以岛中乏食。屡请易粮。本国许发一万七千石。已令饷。臣日夜督运。不谓总镇遽遭肘腋之变。当此之际。若复仍旧输粟。以饷乱众。是助逆而养奸也。倘 皇朝有闻。责以正义。本国将何辞以对乎。夫岛中数万人众。必有忼慨扼腕。思为总镇报仇者。如能昭明大义。声罪致讨。缚取元恶。传示本国。使逆顺暴著于远迩。则本国敢不敦好如旧。不然。本国唯知遵 皇命。致王法而已。宁与贵岛告绝。不忍与犯上无义者。私相比周。以乱 皇朝之纲纪。檄至。岛中皆震惧。复龙之位。还其印绶。龙差
中。世魁三战三破之。及潮退。世魁凯还。 王闻之。又输粟一万七千石以饷之。岛中将士。阴附虏。乃缚龙。夺其印绶。岛中又乱。 王命政府。又为檄谕东江曰。往岁兴治害主将。本国举义致天讨。此贵岛之所明知也。总镇黄公受 天子明命。挂印建牙。来镇东江。此实 皇朝之命帅。全岛之司命也。虽戎政失宜。士心不附。自 朝廷议其得失可也。其在部下。唯当恪守分义而已。今者偏裨倡乱。敢行无道。执缚拘囚。夺其印绶。掠其财贿。虽大盗。何以加此。夫总镇名位之隆。非陈将之比。而缚之与杀。相去无几。则今者之变。比诸兴治。宁有间乎。顷者。总镇以岛中乏食。屡请易粮。本国许发一万七千石。已令饷。臣日夜督运。不谓总镇遽遭肘腋之变。当此之际。若复仍旧输粟。以饷乱众。是助逆而养奸也。倘 皇朝有闻。责以正义。本国将何辞以对乎。夫岛中数万人众。必有忼慨扼腕。思为总镇报仇者。如能昭明大义。声罪致讨。缚取元恶。传示本国。使逆顺暴著于远迩。则本国敢不敦好如旧。不然。本国唯知遵 皇命。致王法而已。宁与贵岛告绝。不忍与犯上无义者。私相比周。以乱 皇朝之纲纪。檄至。岛中皆震惧。复龙之位。还其印绶。龙差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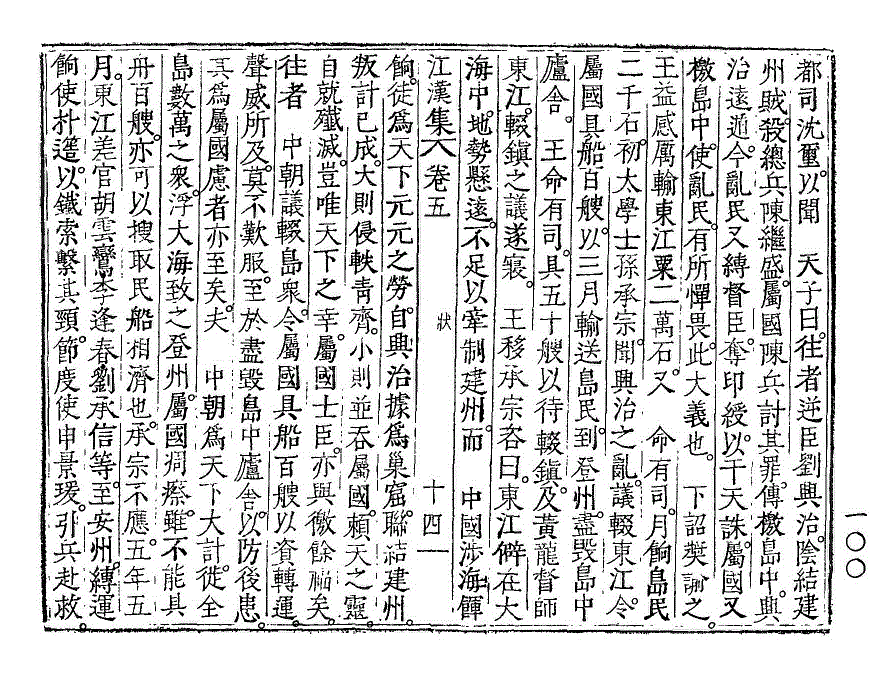 都司沈玺。以闻 天子曰。往者逆臣刘兴治。阴结建州贼。杀总兵陈继盛。属国陈兵讨其罪。传檄岛中。兴治远遁。今乱民又缚督臣。夺印绶。以干天诛。属国又檄岛中。使乱民。有所惮畏。此大义也。 下诏奖谕之。王益感厉输东江粟二万石。又 命有司。月饷岛民二千石。初太学士孙承宗。闻兴治之乱。议辍东江。令属国具船百艘。以三月输送岛民。到登州。尽毁岛中庐舍。 王命有司。具五十艘以待辍镇。及黄龙督师东江。辍镇之议遂寝。 王移承宗咨曰。东江僻在大海中。地势悬远。不足以牵制建州。而 中国涉海餫饷。徒为天下元元之劳。自兴治据为巢窟。联结建州。叛计已成。大则侵轶青齐。小则并吞属国。赖天之灵。自就歼灭。岂唯天下之幸。属国士臣。亦与徼馀福矣。往者 中朝议辍岛众。令属国具船百艘以资转运。声威所及。莫不叹服。至于尽毁岛中庐舍。以防后患。其为属国虑者亦至矣。夫 中朝为天下大计。徙全岛数万之众。浮大海致之登州。属国凋瘵。虽不能具舟百艘。亦可以搜取民船相济也。承宗不应。五年五月。东江差官胡云鸾,李逢春,刘承信等。至安州。缚运饷使朴簉。以铁索系其颈。节度使申景瑗。引兵赴救。
都司沈玺。以闻 天子曰。往者逆臣刘兴治。阴结建州贼。杀总兵陈继盛。属国陈兵讨其罪。传檄岛中。兴治远遁。今乱民又缚督臣。夺印绶。以干天诛。属国又檄岛中。使乱民。有所惮畏。此大义也。 下诏奖谕之。王益感厉输东江粟二万石。又 命有司。月饷岛民二千石。初太学士孙承宗。闻兴治之乱。议辍东江。令属国具船百艘。以三月输送岛民。到登州。尽毁岛中庐舍。 王命有司。具五十艘以待辍镇。及黄龙督师东江。辍镇之议遂寝。 王移承宗咨曰。东江僻在大海中。地势悬远。不足以牵制建州。而 中国涉海餫饷。徒为天下元元之劳。自兴治据为巢窟。联结建州。叛计已成。大则侵轶青齐。小则并吞属国。赖天之灵。自就歼灭。岂唯天下之幸。属国士臣。亦与徼馀福矣。往者 中朝议辍岛众。令属国具船百艘以资转运。声威所及。莫不叹服。至于尽毁岛中庐舍。以防后患。其为属国虑者亦至矣。夫 中朝为天下大计。徙全岛数万之众。浮大海致之登州。属国凋瘵。虽不能具舟百艘。亦可以搜取民船相济也。承宗不应。五年五月。东江差官胡云鸾,李逢春,刘承信等。至安州。缚运饷使朴簉。以铁索系其颈。节度使申景瑗。引兵赴救。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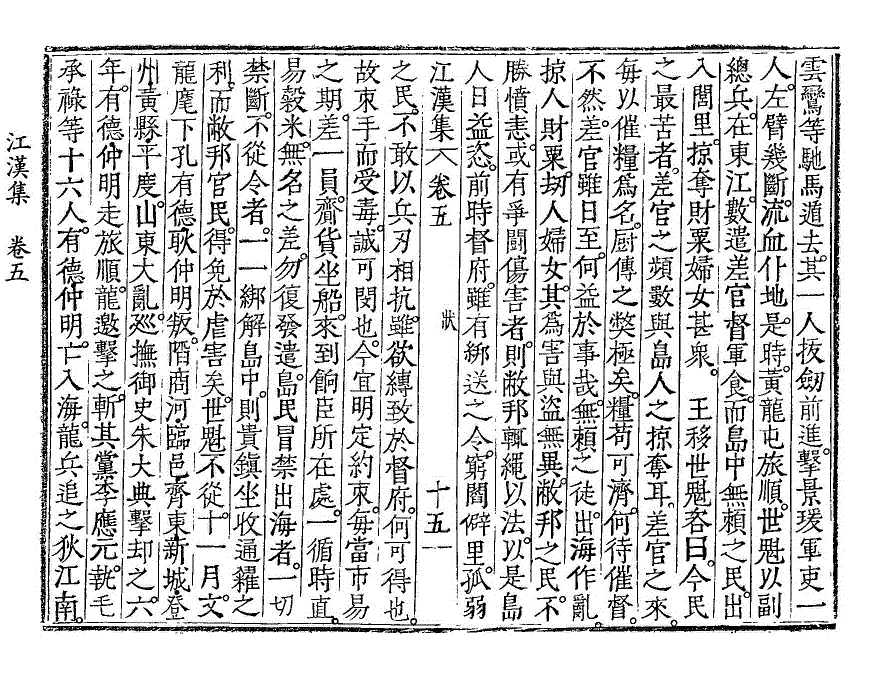 云鸾等驰马遁去。其一人拔剑前进。击景瑗军吏一人。左臂几断。流血仆地。是时。黄龙屯旅顺。世魁以副总兵。在东江。数遣差官督军食。而岛中无赖之民。出入闾里。掠夺财粟妇女甚众。 王移世魁咨曰。今民之最苦者。差官之频数与岛人之掠夺耳。差官之来。每以催粮为名。厨传之弊极矣。粮苟可济。何待催督。不然。差官虽日至。何益于事哉。无赖之徒。出海作乱。掠人财粟。劫人妇女。其为害与盗无异。敝邦之民。不胜愤恚。或有争斗伤害者。则敝邦辄绳以法。以是岛人日益恣。前时督府。虽有绑送之令。穷阎僻里。孤弱之民。不敢以兵刃相抗。虽欲缚致于督府。何可得也。故束手而受毒。诚可闵也。今宜明定约束。每当市易之期。差一员。赍货坐船。来到饷臣所在处。一循时直。易谷米。无名之差。勿复发遣。岛民冒禁出海者。一切禁断。不从令者。一一绑解岛中。则贵镇坐收通籴之利。而敝邦官民。得免于虐害矣。世魁不从。十一月。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叛。陷商河,临邑,齐东,新城,登州,黄县,平度。山东大乱。巡抚御史朱大典击却之。六年。有德,仲明走旅顺。龙邀击之。斩其党李应元。执毛承禄等十六人。有德,仲明。亡入海。龙兵追之狄江南。
云鸾等驰马遁去。其一人拔剑前进。击景瑗军吏一人。左臂几断。流血仆地。是时。黄龙屯旅顺。世魁以副总兵。在东江。数遣差官督军食。而岛中无赖之民。出入闾里。掠夺财粟妇女甚众。 王移世魁咨曰。今民之最苦者。差官之频数与岛人之掠夺耳。差官之来。每以催粮为名。厨传之弊极矣。粮苟可济。何待催督。不然。差官虽日至。何益于事哉。无赖之徒。出海作乱。掠人财粟。劫人妇女。其为害与盗无异。敝邦之民。不胜愤恚。或有争斗伤害者。则敝邦辄绳以法。以是岛人日益恣。前时督府。虽有绑送之令。穷阎僻里。孤弱之民。不敢以兵刃相抗。虽欲缚致于督府。何可得也。故束手而受毒。诚可闵也。今宜明定约束。每当市易之期。差一员。赍货坐船。来到饷臣所在处。一循时直。易谷米。无名之差。勿复发遣。岛民冒禁出海者。一切禁断。不从令者。一一绑解岛中。则贵镇坐收通籴之利。而敝邦官民。得免于虐害矣。世魁不从。十一月。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叛。陷商河,临邑,齐东,新城,登州,黄县,平度。山东大乱。巡抚御史朱大典击却之。六年。有德,仲明走旅顺。龙邀击之。斩其党李应元。执毛承禄等十六人。有德,仲明。亡入海。龙兵追之狄江南。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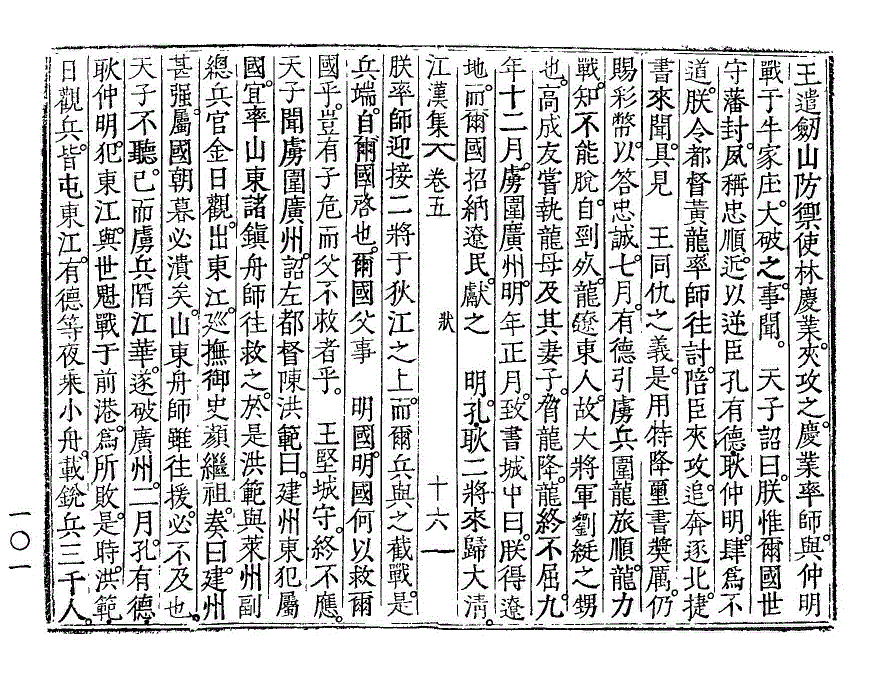 王遣剑山防御使林庆业。夹攻之。庆业率师。与仲明战于牛家庄。大破之。事闻。 天子诏曰。朕惟尔国世守藩封。夙称忠顺。近以逆臣孔有德,耿仲明。肆为不道。朕令都督黄龙率师往讨。陪臣夹攻。追奔逐北。捷书来闻。具见 王同仇之义。是用特降玺书奖厉。仍赐彩币。以答忠诚。七月。有德引虏兵围龙旅顺。龙力战。知不能脱。自刭死。龙辽东人。故大将军刘綎之甥也。高成友尝执龙母及其妻子。胁龙降。龙终不屈。九年十二月。虏围广州。明年正月。致书城中曰。朕得辽地。而尔国招纳辽民。献之 明。孔,耿二将来归大清。朕率师迎接二将于狄江之上。而尔兵与之截战。是兵端。自尔国启也。尔国父事 明国。明国何以救尔国乎。岂有子危而父不救者乎。 王坚城守。终不应。天子闻虏围广州。诏左都督陈洪范曰。建州东犯属国。宜率山东诸镇舟师往救之。于是洪范与莱州副总兵官金日观。出东江。巡抚御史颜继祖。奏曰。建州甚强。属国朝暮必溃矣。山东舟师虽往援。必不及也。天子不听。已而虏兵陷江华。遂破广州。二月。孔有德,耿仲明。犯东江。与世魁战于前港。为所败。是时。洪范,日观兵。皆屯东江。有德等夜乘小舟。载锐兵三千人。
王遣剑山防御使林庆业。夹攻之。庆业率师。与仲明战于牛家庄。大破之。事闻。 天子诏曰。朕惟尔国世守藩封。夙称忠顺。近以逆臣孔有德,耿仲明。肆为不道。朕令都督黄龙率师往讨。陪臣夹攻。追奔逐北。捷书来闻。具见 王同仇之义。是用特降玺书奖厉。仍赐彩币。以答忠诚。七月。有德引虏兵围龙旅顺。龙力战。知不能脱。自刭死。龙辽东人。故大将军刘綎之甥也。高成友尝执龙母及其妻子。胁龙降。龙终不屈。九年十二月。虏围广州。明年正月。致书城中曰。朕得辽地。而尔国招纳辽民。献之 明。孔,耿二将来归大清。朕率师迎接二将于狄江之上。而尔兵与之截战。是兵端。自尔国启也。尔国父事 明国。明国何以救尔国乎。岂有子危而父不救者乎。 王坚城守。终不应。天子闻虏围广州。诏左都督陈洪范曰。建州东犯属国。宜率山东诸镇舟师往救之。于是洪范与莱州副总兵官金日观。出东江。巡抚御史颜继祖。奏曰。建州甚强。属国朝暮必溃矣。山东舟师虽往援。必不及也。天子不听。已而虏兵陷江华。遂破广州。二月。孔有德,耿仲明。犯东江。与世魁战于前港。为所败。是时。洪范,日观兵。皆屯东江。有德等夜乘小舟。载锐兵三千人。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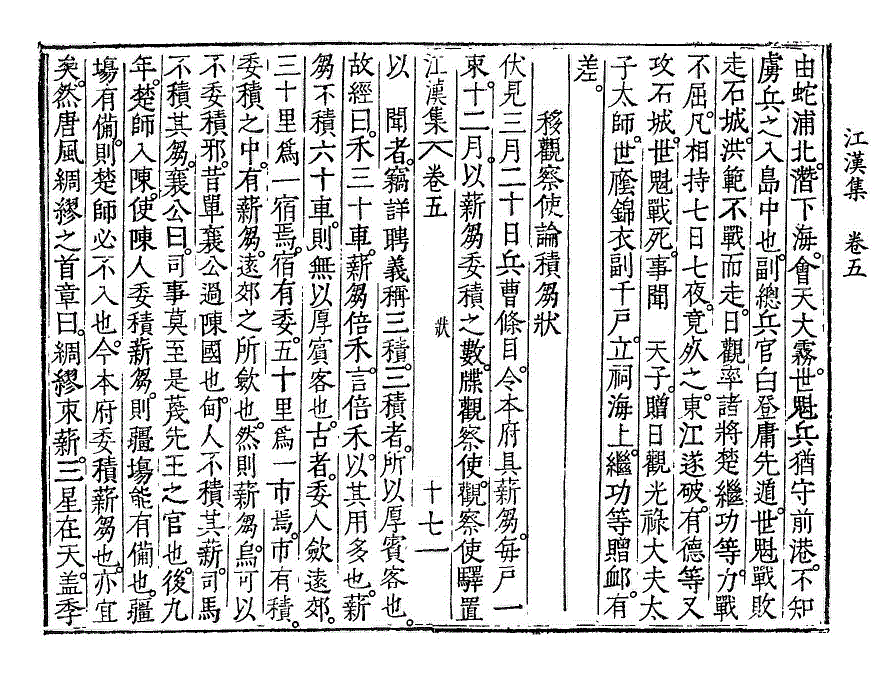 由蛇浦北。潜下海。会天大雾。世魁兵犹守前港。不知虏兵之入岛中也。副总兵官白登庸先遁。世魁战败走石城。洪范不战而走。日观率诸将楚继功等。力战不屈。凡相持七日七夜。竟死之。东江遂破。有德等又攻石城。世魁战死。事闻 天子。赠日观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世荫锦衣副千户。立祠海上。继功等赠恤。有差。
由蛇浦北。潜下海。会天大雾。世魁兵犹守前港。不知虏兵之入岛中也。副总兵官白登庸先遁。世魁战败走石城。洪范不战而走。日观率诸将楚继功等。力战不屈。凡相持七日七夜。竟死之。东江遂破。有德等又攻石城。世魁战死。事闻 天子。赠日观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世荫锦衣副千户。立祠海上。继功等赠恤。有差。移观察使论积刍状
伏见三月二十日兵曹条目。令本府具薪刍。每户一束。十二月。以薪刍委积之数。牒观察使。观察使驿置以 闻者。窃详聘义称三积。三积者。所以厚宾客也。故经曰。禾三十车。薪刍倍禾。言倍禾。以其用多也。薪刍不积六十车。则无以厚宾客也。古者。委人敛远郊。三十里为一宿焉。宿有委。五十里为一市焉。市有积。委积之中。有薪刍。远郊之所敛也。然则薪刍。乌可以不委积邪。昔单襄公过陈国也。甸人不积其薪。司马不积其刍。襄公曰。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后九年。楚师入陈。使陈人委积薪刍。则疆场能有备也。疆场有备。则楚师必不入也。今本府委积薪刍也。亦宜矣。然唐风绸缪之首章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盖季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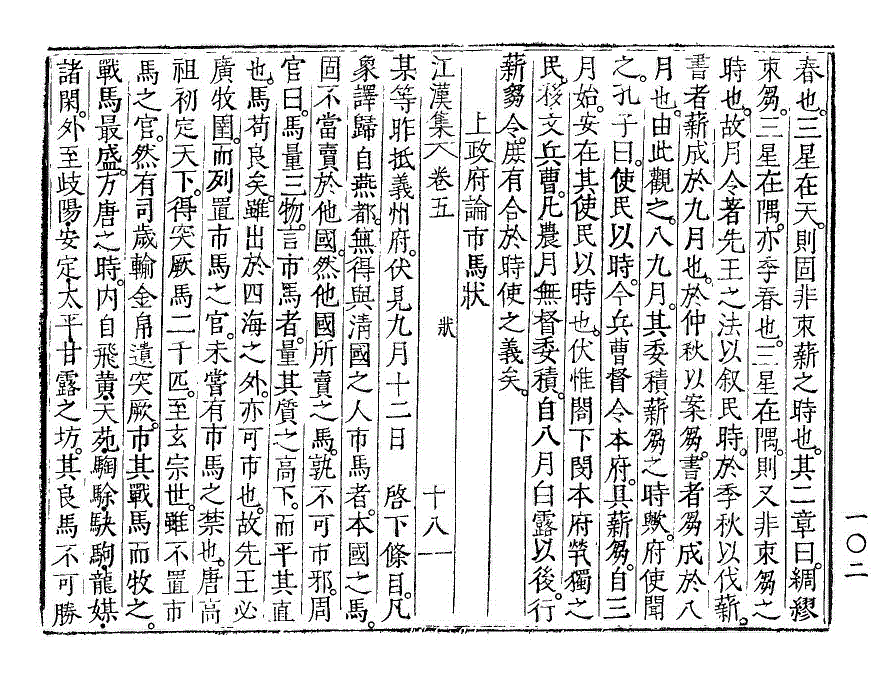 春也。三星在天。则固非束薪之时也。其二章曰。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亦季春也。三星在隅。则又非束刍之时也。故月令著先王之法以叙民时。于季秋以伐薪。书者薪成于九月也。于仲秋以案刍。书者刍成于八月也。由此观之。八九月。其委积薪刍之时欤。府使闻之。孔子曰。使民以时。今兵曹督令本府。具薪刍。自三月始。安在其使民以时也。伏惟閤下闵本府煢独之民。移文兵曹。凡农月无督委积。自八月白露以后。行薪刍令。庶有合于时使之义矣。
春也。三星在天。则固非束薪之时也。其二章曰。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亦季春也。三星在隅。则又非束刍之时也。故月令著先王之法以叙民时。于季秋以伐薪。书者薪成于九月也。于仲秋以案刍。书者刍成于八月也。由此观之。八九月。其委积薪刍之时欤。府使闻之。孔子曰。使民以时。今兵曹督令本府。具薪刍。自三月始。安在其使民以时也。伏惟閤下闵本府煢独之民。移文兵曹。凡农月无督委积。自八月白露以后。行薪刍令。庶有合于时使之义矣。上政府论市马状
某等昨抵义州府。伏见九月十二日 启下条目。凡象译归自燕都。无得与清国之人市马者。本国之马。固不当卖于他国。然他国所卖之马。孰不可市邪。周官曰。马量三物。言市马者。量其质之高下。而平其直也。马苟良矣。虽出于四海之外。亦可市也。故先王必广牧圉。而列置市马之官。未尝有市马之禁也。唐高祖初定天下。得突厥马二千匹。至玄宗世。虽不置市马之官。然有司岁输金帛遗突厥。市其战马而牧之。战马最盛。方唐之时。内自飞黄,天苑,騊駼,駃驹,龙媒,诸闲。外至歧阳,安定,太平,甘露之坊。其良马不可胜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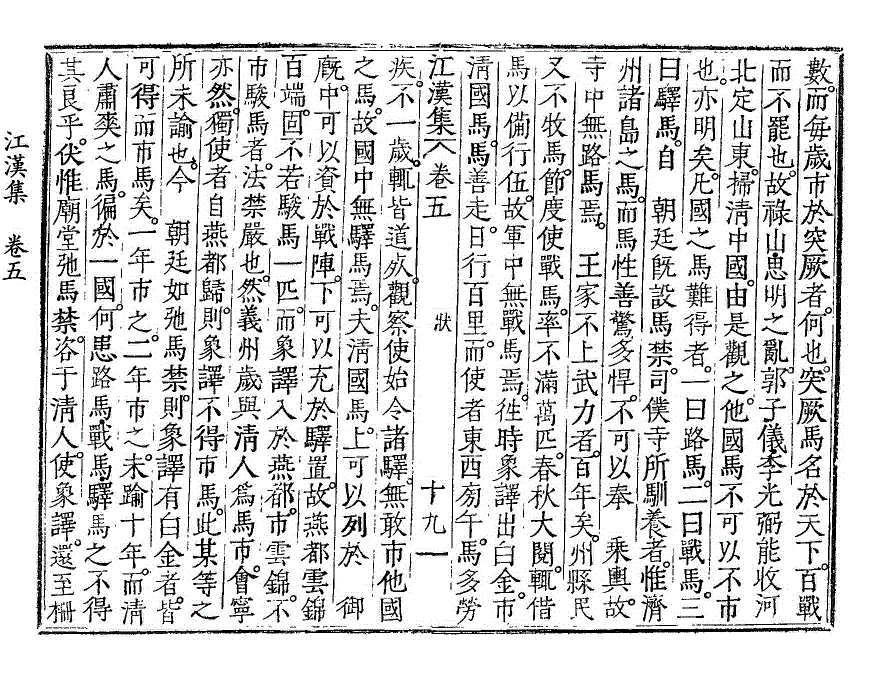 数。而每岁市于突厥者。何也。突厥马名于天下。百战而不罢也。故禄山,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能收河北定山东。扫清中国。由是观之。他国马不可以不市也。亦明矣。凡国之马难得者。一曰路马。二曰战马。三曰驿马。自 朝廷既设马禁。司仆寺所驯养者。惟济州诸岛之马。而马性善惊多悍。不可以奉 乘舆。故寺中无路马焉。 王家不上武力者。百年矣。州县民又不牧马。节度使战马。率不满万匹。春秋大阅。辄借马以备行伍。故军中无战马焉。往时象译出白金。市清国马。马善走。日行百里。而使者东西旁午。马多劳疾。不一岁。辄皆道死。观察使始令诸驿。无敢市他国之马。故国中无驿马焉。夫清国马。上可以列于 御厩。中可以资于战阵。下可以充于驿置。故燕都云锦百端。固不若骏马一匹。而象译入于燕都。市云锦。不市骏马者。法禁严也。然义州岁与清人为马市。会宁亦然。独使者自燕都归。则象译不得市马。此某等之所未谕也。今 朝廷如弛马禁。则象译有白金者。皆可得而市马矣。一年市之。二年市之。未踰十年。而清人肃爽之马。遍于一国。何患路马,战马,驿马之不得其良乎。伏惟庙堂弛马禁。咨于清人。使象译。还至栅
数。而每岁市于突厥者。何也。突厥马名于天下。百战而不罢也。故禄山,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能收河北定山东。扫清中国。由是观之。他国马不可以不市也。亦明矣。凡国之马难得者。一曰路马。二曰战马。三曰驿马。自 朝廷既设马禁。司仆寺所驯养者。惟济州诸岛之马。而马性善惊多悍。不可以奉 乘舆。故寺中无路马焉。 王家不上武力者。百年矣。州县民又不牧马。节度使战马。率不满万匹。春秋大阅。辄借马以备行伍。故军中无战马焉。往时象译出白金。市清国马。马善走。日行百里。而使者东西旁午。马多劳疾。不一岁。辄皆道死。观察使始令诸驿。无敢市他国之马。故国中无驿马焉。夫清国马。上可以列于 御厩。中可以资于战阵。下可以充于驿置。故燕都云锦百端。固不若骏马一匹。而象译入于燕都。市云锦。不市骏马者。法禁严也。然义州岁与清人为马市。会宁亦然。独使者自燕都归。则象译不得市马。此某等之所未谕也。今 朝廷如弛马禁。则象译有白金者。皆可得而市马矣。一年市之。二年市之。未踰十年。而清人肃爽之马。遍于一国。何患路马,战马,驿马之不得其良乎。伏惟庙堂弛马禁。咨于清人。使象译。还至栅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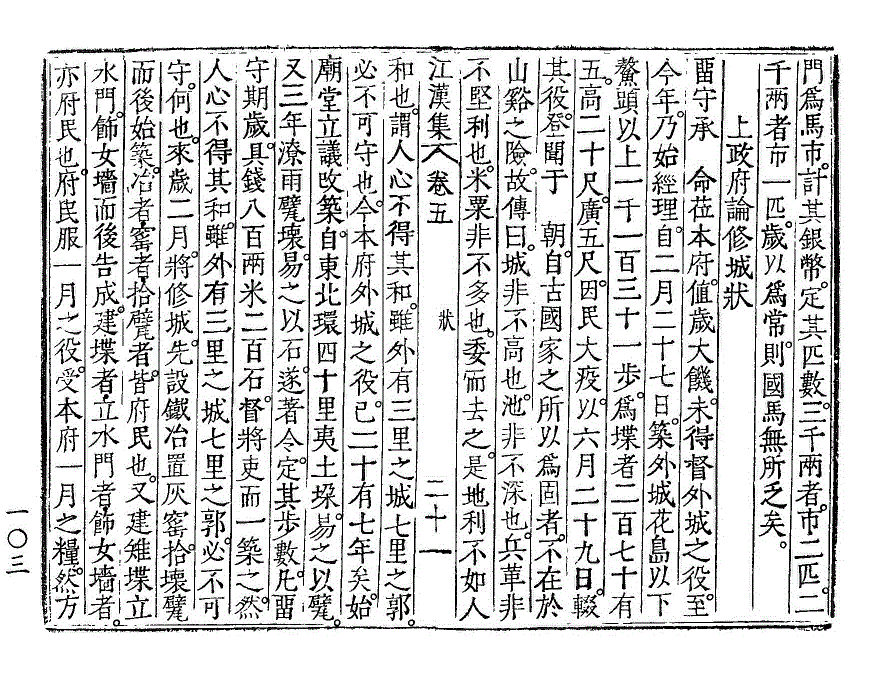 门为马市。计其银币。定其匹数。三千两者。市二匹。二千两者市一匹。岁以为常。则国马无所乏矣。
门为马市。计其银币。定其匹数。三千两者。市二匹。二千两者市一匹。岁以为常。则国马无所乏矣。上政府论修城状
留守承 命莅本府。值岁大饥。未得督外城之役。至今年。乃始经理。自二月二十七日。筑外城花岛以下鳌头以上一千一百三十一步。为堞者二百七十有五。高二十尺。广五尺。因民大疫。以六月二十九日。辍其役。登闻于 朝。自古国家之所以为固者。不在于山溪之险。故传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谓人心不得其和。虽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也。今本府外城之役。已二十有七年矣。始庙堂立议改筑。自东北环四十里夷土垛。易之以甓。又三年潦雨甓坏。易之以石。遂著令。定其步数。凡留守期岁。具钱八百两米二百石。督将吏而一筑之。然人心不得其和。虽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何也。来岁二月。将修城。先设铁冶置灰窑。拾坏甓而后始筑。冶者,窑者,拾甓者。皆府民也。又建雉堞立水门。饰女墙而后告成。建堞者,立水门者,饰女墙者。亦府民也。府民服一月之役。受本府一月之粮。然方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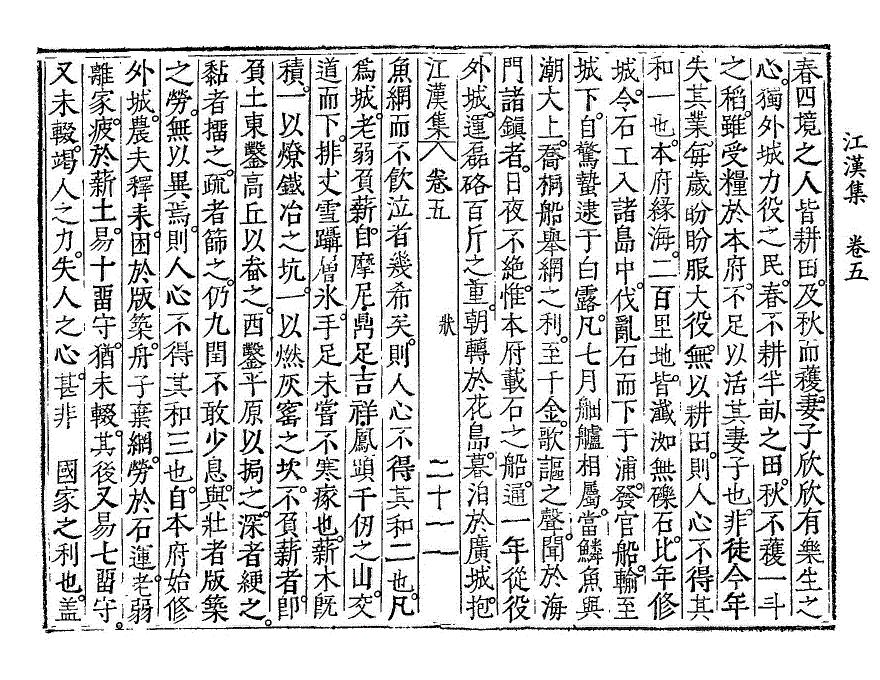 春四境之人皆耕田。及秋而穫。妻子欣欣有乐生之心。独外城力役之民。春不耕半亩之田。秋不穫一斗之稻。虽受粮于本府。不足以活其妻子也。非徒今年失其业。每岁盼盼服大役。无以耕田。则人心不得其和一也。本府缘海。二百里地。皆瀸洳无砾石。比年修城。令石工入诸岛中。伐乱石而下于浦。发官船。输至城下。自惊蛰逮于白露。凡七月舳舻相属。当鳞鱼与潮大上。乔桐船举网之利。至千金。歌讴之声。闻于海门诸镇者。日夜不绝。惟本府载石之船。通一年从役外城。运磊硌百斤之重。朝转于花岛。暮泊于广城。抱鱼网而不饮泣者几希矣。则人心不得其和二也。凡为城。老弱负薪。自摩尼,鼎足,吉祥,凤头千仞之山。交道而下。排丈雪蹑层冰。手足未尝不寒瘃也。薪木既积。一以燎铁冶之坑。一以燃灰窑之坎。不负薪者。即负土东凿高丘以畚之。西凿平原以挶之。深者绠之。黏者㨨之。疏者筛之。仍九闰不敢少息。与壮者版筑之劳。无以异焉。则人心不得其和三也。自本府始修外城。农夫释耒。困于版筑。舟子弃网。劳于石运。老弱离家。疲于薪土。易十留守。犹未辍。其后又易七留守。又未辍。竭人之力。失人之心。甚非 国家之利也。盖
春四境之人皆耕田。及秋而穫。妻子欣欣有乐生之心。独外城力役之民。春不耕半亩之田。秋不穫一斗之稻。虽受粮于本府。不足以活其妻子也。非徒今年失其业。每岁盼盼服大役。无以耕田。则人心不得其和一也。本府缘海。二百里地。皆瀸洳无砾石。比年修城。令石工入诸岛中。伐乱石而下于浦。发官船。输至城下。自惊蛰逮于白露。凡七月舳舻相属。当鳞鱼与潮大上。乔桐船举网之利。至千金。歌讴之声。闻于海门诸镇者。日夜不绝。惟本府载石之船。通一年从役外城。运磊硌百斤之重。朝转于花岛。暮泊于广城。抱鱼网而不饮泣者几希矣。则人心不得其和二也。凡为城。老弱负薪。自摩尼,鼎足,吉祥,凤头千仞之山。交道而下。排丈雪蹑层冰。手足未尝不寒瘃也。薪木既积。一以燎铁冶之坑。一以燃灰窑之坎。不负薪者。即负土东凿高丘以畚之。西凿平原以挶之。深者绠之。黏者㨨之。疏者筛之。仍九闰不敢少息。与壮者版筑之劳。无以异焉。则人心不得其和三也。自本府始修外城。农夫释耒。困于版筑。舟子弃网。劳于石运。老弱离家。疲于薪土。易十留守。犹未辍。其后又易七留守。又未辍。竭人之力。失人之心。甚非 国家之利也。盖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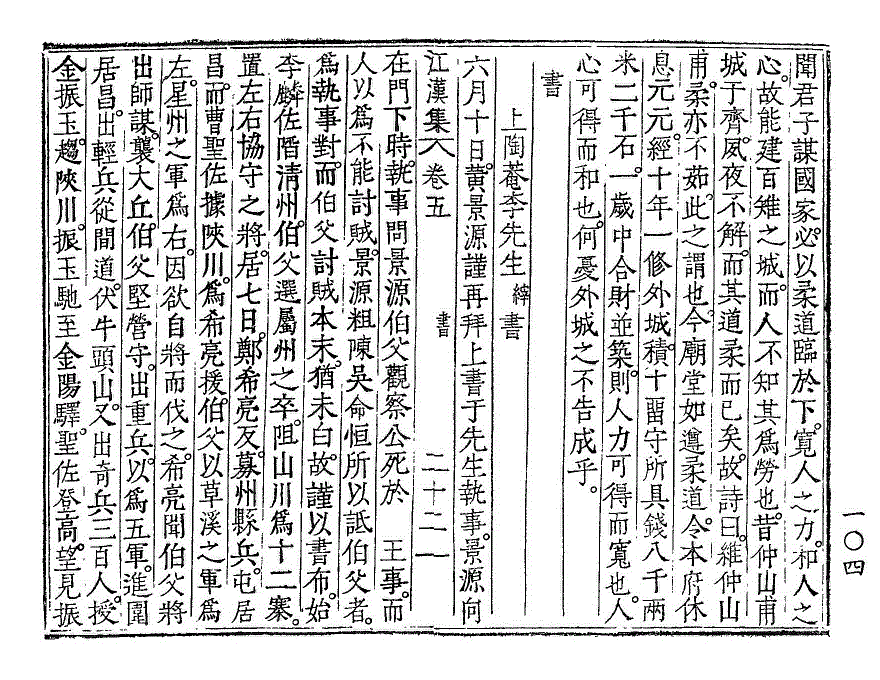 闻君子谋国家。必以柔道临于下。宽人之力。和人之心。故能建百雉之城。而人不知其为劳也。昔仲山甫城于齐。夙夜不解。而其道柔而已矣。故诗曰。维仲山甫。柔亦不茹。此之谓也。今庙堂如遵柔道。令本府休息元元。经十年一修外城。积十留守所具钱八千两米二千石。一岁中合财并筑。则人力可得而宽也。人心可得而和也。何忧外城之不告成乎。
闻君子谋国家。必以柔道临于下。宽人之力。和人之心。故能建百雉之城。而人不知其为劳也。昔仲山甫城于齐。夙夜不解。而其道柔而已矣。故诗曰。维仲山甫。柔亦不茹。此之谓也。今庙堂如遵柔道。令本府休息元元。经十年一修外城。积十留守所具钱八千两米二千石。一岁中合财并筑。则人力可得而宽也。人心可得而和也。何忧外城之不告成乎。江汉集卷之五
书
上陶庵李先生(縡)书
六月十日。黄景源谨再拜上书于先生执事。景源向在门下时。执事问景源伯父观察公死于 王事。而人以为不能讨贼。景源粗陈吴命恒所以诋伯父者。为执事对。而伯父讨贼本末。犹未白。故谨以书布。始李麟佐陷清州。伯父选属州之卒。阻山川为十二寨。置左右协守之将。居七日。郑希亮反。募州县兵。屯居昌。而曹圣佐据陜川。为希亮援。伯父以草溪之军为左。星州之军为右。因欲自将而伐之。希亮闻伯父将出师谋。袭大丘。伯父坚营守。出重兵。以为五军。进围居昌。出轻兵从间道。伏牛头山。又出奇兵三百人。授金振玉。趋陜川。振玉驰至金阳驿。圣佐登高。望见振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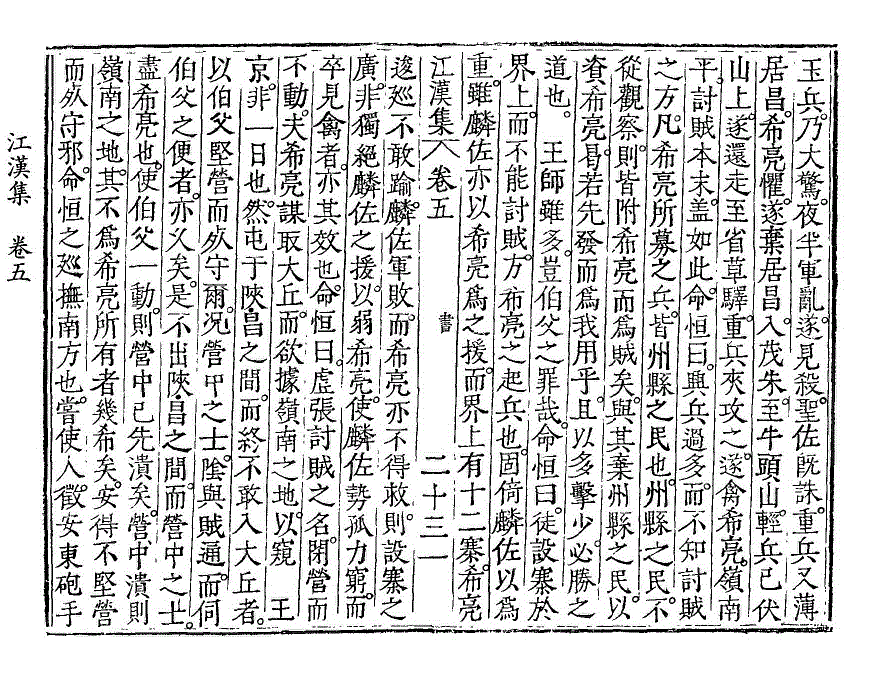 玉兵。乃大惊。夜半军乱。遂见杀。圣佐既诛。重兵又薄居昌。希亮惧。遂弃居昌。入茂朱。至牛头山。轻兵已伏山上。遂还走至省草驿。重兵夹攻之。遂禽希亮。岭南平。讨贼本末。盖如此。命恒曰。兴兵过多。而不知讨贼之方。凡希亮所募之兵。皆州县之民也。州县之民。不从观察。则皆附希亮而为贼矣。与其弃州县之民。以资希亮。曷若先发而为我用乎。且以多击少。必胜之道也。 王师虽多。岂伯父之罪哉。命恒曰。徒设寨于界上。而不能讨贼。方希亮之起兵也。固倚麟佐以为重。虽麟佐亦以希亮为之援。而界上有十二寨。希亮逡巡不敢踰。麟佐军败。而希亮亦不得救。则设寨之广。非独绝麟佐之援。以弱希亮。使麟佐势孤力穷。而卒见禽者。亦其效也。命恒曰。虚张讨贼之名。闭营而不动。夫希亮谋取大丘。而欲据岭南之地。以窥 王京。非一日也。然屯于陜,昌之间。而终不敢入大丘者。以伯父坚营而死守尔。况营中之士。阴与贼通。而伺伯父之便者。亦久矣。是不出陜,昌之间。而营中之士。尽希亮也。使伯父一动。则营中已先溃矣。营中溃则岭南之地。其不为希亮所有者几希矣。安得不坚营而死守邪。命恒之巡抚南方也。尝使人。徵安东炮手
玉兵。乃大惊。夜半军乱。遂见杀。圣佐既诛。重兵又薄居昌。希亮惧。遂弃居昌。入茂朱。至牛头山。轻兵已伏山上。遂还走至省草驿。重兵夹攻之。遂禽希亮。岭南平。讨贼本末。盖如此。命恒曰。兴兵过多。而不知讨贼之方。凡希亮所募之兵。皆州县之民也。州县之民。不从观察。则皆附希亮而为贼矣。与其弃州县之民。以资希亮。曷若先发而为我用乎。且以多击少。必胜之道也。 王师虽多。岂伯父之罪哉。命恒曰。徒设寨于界上。而不能讨贼。方希亮之起兵也。固倚麟佐以为重。虽麟佐亦以希亮为之援。而界上有十二寨。希亮逡巡不敢踰。麟佐军败。而希亮亦不得救。则设寨之广。非独绝麟佐之援。以弱希亮。使麟佐势孤力穷。而卒见禽者。亦其效也。命恒曰。虚张讨贼之名。闭营而不动。夫希亮谋取大丘。而欲据岭南之地。以窥 王京。非一日也。然屯于陜,昌之间。而终不敢入大丘者。以伯父坚营而死守尔。况营中之士。阴与贼通。而伺伯父之便者。亦久矣。是不出陜,昌之间。而营中之士。尽希亮也。使伯父一动。则营中已先溃矣。营中溃则岭南之地。其不为希亮所有者几希矣。安得不坚营而死守邪。命恒之巡抚南方也。尝使人。徵安东炮手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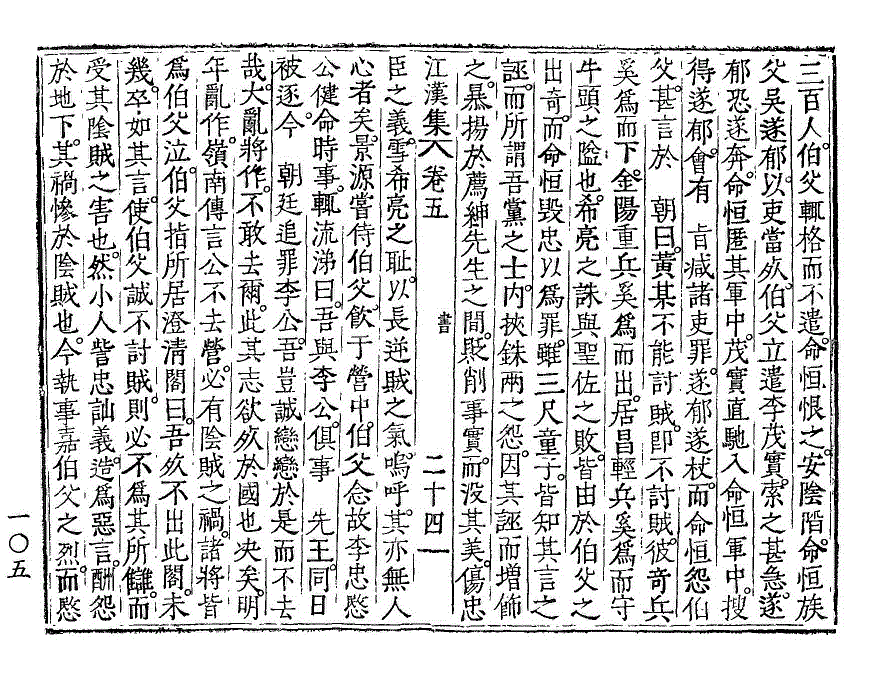 三百人。伯父辄格而不遣。命恒恨之。安阴陷。命恒族父吴遂郁。以吏当死。伯父立遣李茂实。索之甚急。遂郁恐遂奔。命恒匿其军中。茂实直驰入命恒军中。搜得遂郁。会有 旨减诸吏罪。遂郁遂杖。而命恒怨伯父。甚言于 朝曰。黄某不能讨贼。即不讨贼。彼奇兵奚为而下。金阳重兵奚为而出。居昌轻兵奚为而守牛头之隘也。希亮之诛与圣佐之败。皆由于伯父之出奇。而命恒毁忠以为罪。虽三尺童子。皆知其言之诬。而所谓吾党之士。内挟铢两之怨。因其诬而增饰之。暴扬于荐绅先生之间。贬削事实。而没其美。伤忠臣之义。雪希亮之耻。以长逆贼之气。呜呼。其亦无人心者矣。景源尝侍伯父。饮于营中。伯父念故李忠悯公健命时事。辄流涕曰。吾与李公。俱事 先王。同日被逐。今 朝廷追罪李公。吾岂诚恋恋于是而不去哉。大乱将作。不敢去尔。此其志欲死于国也决矣。明年乱作。岭南传言公不去营。必有阴贼之祸。诸将皆为伯父泣。伯父指所居澄清阁曰。吾死不出此阁。未几。卒如其言。使伯父诚不讨贼。则必不为其所雠。而受其阴贼之害也。然小人訾忠讪义。造为恶言。酬怨于地下。其祸惨于阴贼也。今执事嘉伯父之烈。而悯
三百人。伯父辄格而不遣。命恒恨之。安阴陷。命恒族父吴遂郁。以吏当死。伯父立遣李茂实。索之甚急。遂郁恐遂奔。命恒匿其军中。茂实直驰入命恒军中。搜得遂郁。会有 旨减诸吏罪。遂郁遂杖。而命恒怨伯父。甚言于 朝曰。黄某不能讨贼。即不讨贼。彼奇兵奚为而下。金阳重兵奚为而出。居昌轻兵奚为而守牛头之隘也。希亮之诛与圣佐之败。皆由于伯父之出奇。而命恒毁忠以为罪。虽三尺童子。皆知其言之诬。而所谓吾党之士。内挟铢两之怨。因其诬而增饰之。暴扬于荐绅先生之间。贬削事实。而没其美。伤忠臣之义。雪希亮之耻。以长逆贼之气。呜呼。其亦无人心者矣。景源尝侍伯父。饮于营中。伯父念故李忠悯公健命时事。辄流涕曰。吾与李公。俱事 先王。同日被逐。今 朝廷追罪李公。吾岂诚恋恋于是而不去哉。大乱将作。不敢去尔。此其志欲死于国也决矣。明年乱作。岭南传言公不去营。必有阴贼之祸。诸将皆为伯父泣。伯父指所居澄清阁曰。吾死不出此阁。未几。卒如其言。使伯父诚不讨贼。则必不为其所雠。而受其阴贼之害也。然小人訾忠讪义。造为恶言。酬怨于地下。其祸惨于阴贼也。今执事嘉伯父之烈。而悯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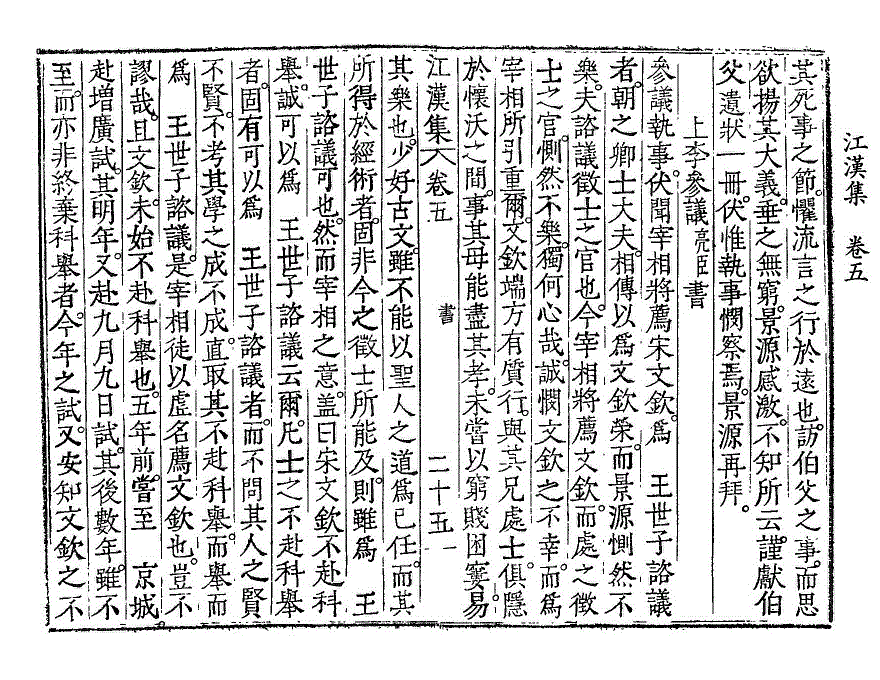 其死事之节。惧流言之行于远也。访伯父之事。而思欲扬其大义。垂之无穷。景源感激。不知所云。谨献伯父遗状一册。伏惟执事悯察焉。景源再拜。
其死事之节。惧流言之行于远也。访伯父之事。而思欲扬其大义。垂之无穷。景源感激。不知所云。谨献伯父遗状一册。伏惟执事悯察焉。景源再拜。上李参议(亮臣)书
参议执事。伏闻宰相将荐宋文钦。为 王世子咨议者。朝之卿士大夫。相传以为文钦荣。而景源恻然不乐。夫咨议徵士之官也。今宰相将荐文钦。而处之徵士之官。恻然不乐。独何心哉。诚悯文钦之不幸。而为宰相所引重尔。文钦端方有质行。与其兄处士。俱隐于怀沃之间。事其母能尽其孝。未尝以穷贱困窭。易其乐也。少好古文。虽不能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而其所得于经术者。固非今之徵士所能及。则虽为 王世子咨议可也。然而宰相之意。盖曰宋文钦不赴科举。诚可以为 王世子咨议云尔。凡士之不赴科举者。固有可以为 王世子咨议者。而不问其人之贤不贤。不考其学之成不成。直取其不赴科举。而举而为 王世子咨议。是宰相徒以虚名荐文钦也。岂不谬哉。且文钦。未始不赴科举也。五年前。尝至 京城。赴增广试。其明年。又赴九月九日试。其后数年。虽不至。而亦非终弃科举者。今年之试。又安知文钦之不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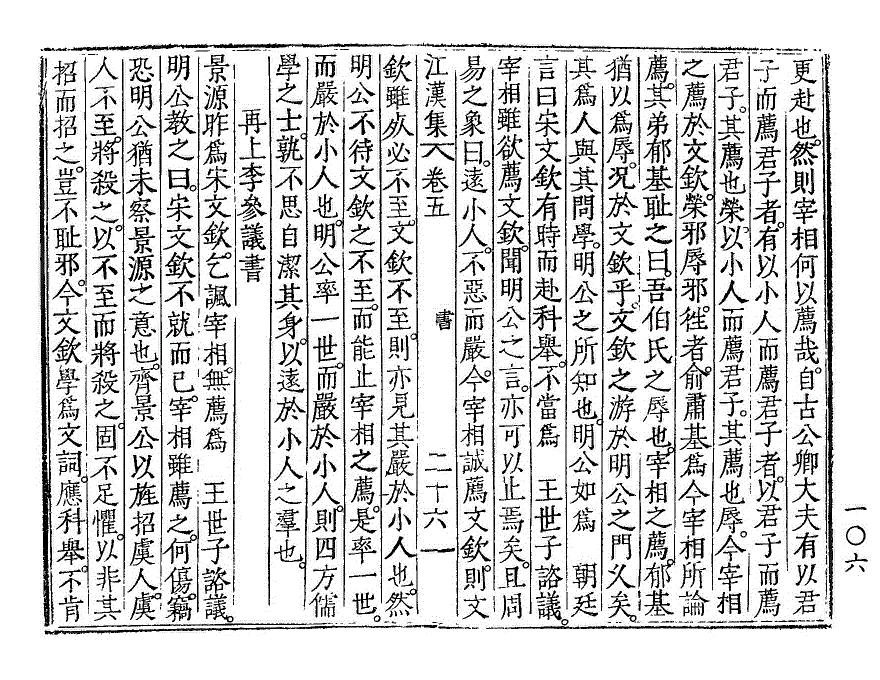 更赴也。然则宰相何以荐哉。自古公卿大夫有以君子而荐君子者。有以小人而荐君子者。以君子而荐君子。其荐也荣。以小人而荐君子。其荐也辱。今宰相之荐于文钦。荣邪辱邪。往者。俞肃基为今宰相所论荐。其弟郁基耻之曰。吾伯氏之辱也。宰相之荐。郁基犹以为辱。况于文钦乎。文钦之游于明公之门久矣。其为人与其问学。明公之所知也。明公如为 朝廷言曰宋文钦有时而赴科举。不当为 王世子咨议。宰相虽欲荐文钦。闻明公之言。亦可以止焉矣。且周易之象曰。远小人。不恶而严。今宰相诚荐文钦。则文钦虽死必不至。文钦不至。则亦见其严于小人也。然明公不待文钦之不至。而能止宰相之荐。是率一世。而严于小人也。明公率一世。而严于小人。则四方儒学之士。孰不思自洁其身。以远于小人之群也。
更赴也。然则宰相何以荐哉。自古公卿大夫有以君子而荐君子者。有以小人而荐君子者。以君子而荐君子。其荐也荣。以小人而荐君子。其荐也辱。今宰相之荐于文钦。荣邪辱邪。往者。俞肃基为今宰相所论荐。其弟郁基耻之曰。吾伯氏之辱也。宰相之荐。郁基犹以为辱。况于文钦乎。文钦之游于明公之门久矣。其为人与其问学。明公之所知也。明公如为 朝廷言曰宋文钦有时而赴科举。不当为 王世子咨议。宰相虽欲荐文钦。闻明公之言。亦可以止焉矣。且周易之象曰。远小人。不恶而严。今宰相诚荐文钦。则文钦虽死必不至。文钦不至。则亦见其严于小人也。然明公不待文钦之不至。而能止宰相之荐。是率一世。而严于小人也。明公率一世。而严于小人。则四方儒学之士。孰不思自洁其身。以远于小人之群也。再上李参议书
景源昨为宋文钦。乞讽宰相。无荐为 王世子咨议。明公教之曰。宋文钦不就而已。宰相虽荐之。何伤。窃恐明公犹未察景源之意也。齐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不至。将杀之。以不至而将杀之。固不足惧。以非其招而招之。岂不耻邪。今文钦学为文词。应科举。不肯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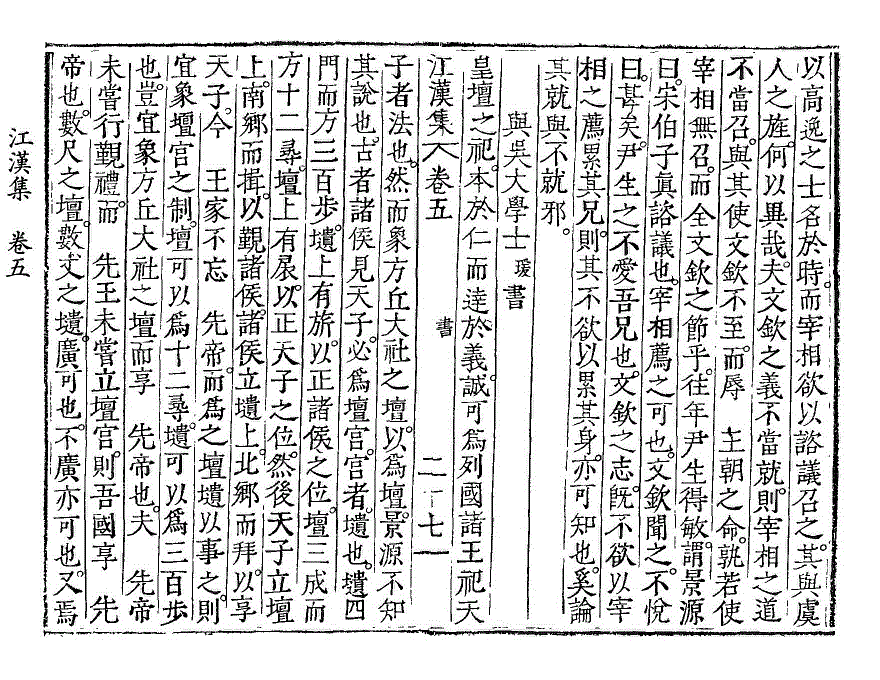 以高逸之士名于时。而宰相欲以咨议召之。其与虞人之旌。何以异哉。夫文钦之义不当就。则宰相之道不当召。与其使文钦不至。而辱 王朝之命。孰若使宰相无召。而全文钦之节乎。往年尹生得敏。谓景源曰。宋伯子真咨议也。宰相荐之可也。文钦闻之。不悦曰。甚矣。尹生之不爱吾兄也。文钦之志。既不欲以宰相之荐累其兄。则其不欲以累其身。亦可知也。奚论其就与不就邪。
以高逸之士名于时。而宰相欲以咨议召之。其与虞人之旌。何以异哉。夫文钦之义不当就。则宰相之道不当召。与其使文钦不至。而辱 王朝之命。孰若使宰相无召。而全文钦之节乎。往年尹生得敏。谓景源曰。宋伯子真咨议也。宰相荐之可也。文钦闻之。不悦曰。甚矣。尹生之不爱吾兄也。文钦之志。既不欲以宰相之荐累其兄。则其不欲以累其身。亦可知也。奚论其就与不就邪。与吴大学士(瑗)书
皇坛之祀。本于仁而达于义。诚可为列国诸王祀天子者法也。然而象方丘大社之坛。以为坛。景源不知其说也。古者诸侯见天子。必为坛宫。宫者。壝也。壝四门而方三百步。壝上有旂。以正诸侯之位。坛三成而方十二寻。坛上有扆。以正天子之位。然后天子立坛上。南乡而揖。以觐诸侯。诸侯立壝上。北乡而拜。以享天子。今 王家不忘 先帝。而为之坛壝以事之。则宜象坛宫之制。坛可以为十二寻。壝可以为三百步也。岂宜象方丘大社之坛而享 先帝也。夫 先帝未尝行觐礼。而 先王未尝立坛宫。则吾国享 先帝也。数尺之坛。数丈之壝。广可也。不广亦可也。又焉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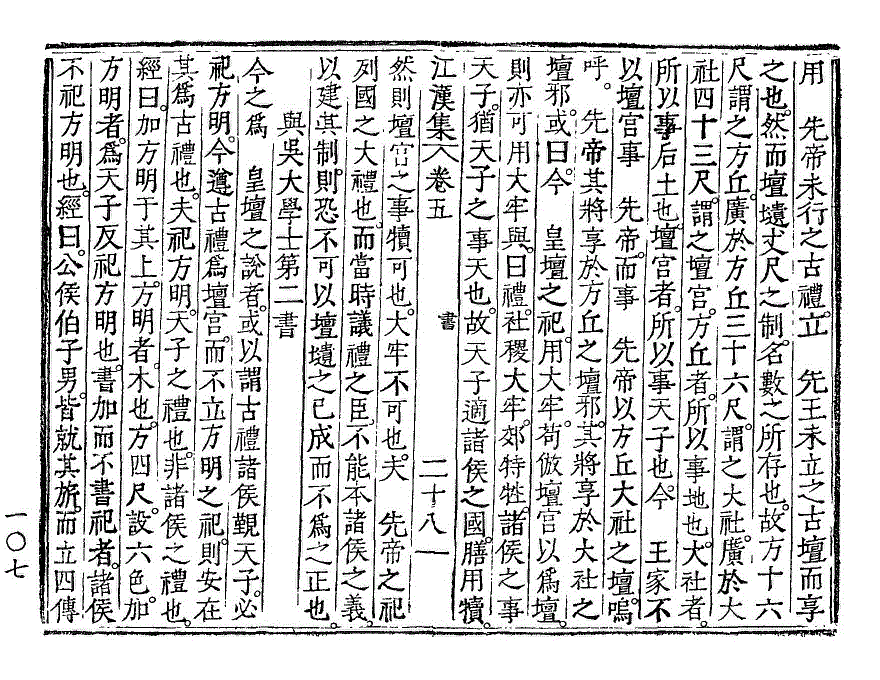 用 先帝未行之古礼。立 先王未立之古坛而享之也。然而坛壝丈尺之制。名数之所存也。故方十六尺谓之方丘。广于方丘三十六尺。谓之大社。广于大社四十三尺。谓之坛宫。方丘者。所以事地也。大社者。所以事后土也。坛宫者。所以事天子也。今 王家不以坛宫事 先帝。而事 先帝以方丘大社之坛。呜呼。 先帝其将享于方丘之坛邪。其将享于大社之坛邪。或曰。今 皇坛之祀。用大牢。苟仿坛宫以为坛。则亦可用大牢与。曰礼。社稷大牢。郊特牲。诸侯之事天子。犹天子之事天也。故天子适诸侯之国。膳用犊。然则坛宫之事犊可也。大牢不可也。夫 先帝之祀列国之大礼也。而当时议礼之臣。不能本诸侯之义。以建其制。则恐不可以坛壝之已成而不为之正也。
用 先帝未行之古礼。立 先王未立之古坛而享之也。然而坛壝丈尺之制。名数之所存也。故方十六尺谓之方丘。广于方丘三十六尺。谓之大社。广于大社四十三尺。谓之坛宫。方丘者。所以事地也。大社者。所以事后土也。坛宫者。所以事天子也。今 王家不以坛宫事 先帝。而事 先帝以方丘大社之坛。呜呼。 先帝其将享于方丘之坛邪。其将享于大社之坛邪。或曰。今 皇坛之祀。用大牢。苟仿坛宫以为坛。则亦可用大牢与。曰礼。社稷大牢。郊特牲。诸侯之事天子。犹天子之事天也。故天子适诸侯之国。膳用犊。然则坛宫之事犊可也。大牢不可也。夫 先帝之祀列国之大礼也。而当时议礼之臣。不能本诸侯之义。以建其制。则恐不可以坛壝之已成而不为之正也。与吴大学士[第二书]
今之为 皇坛之说者。或以谓古礼诸侯觐天子。必祀方明。今遵古礼为坛宫。而不立方明之祀。则安在其为古礼也。夫祀方明。天子之礼也。非诸侯之礼也。经曰。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加方明者。为天子反祀方明也。书加而不书祀者。诸侯不祀方明也。经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8H 页
 摈。传摈者。觐天子也。言传摈而不及方明者。诸侯不敢祀方明也。经曰。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拜日者。已觐诸侯而朝于日也。祀方明者。告于天地四方也。古者。天子觐诸侯。然后拜日。拜日然后祀方明。故曰。祀方明。天子之礼也。非诸侯之礼也。昔鲁公郊祀上帝。又象明堂。作太庙。禘祀文王。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周公之道衰。而鲁始郊禘。然而天下之情无穷。而先王之礼有时乎穷。礼穷则以义起之。以义起之。而能合于先王之意。则君子不以为滥也。使周室既亡之后。文王之庙不血食。而鲁公以旧诸侯祀文王。而不祀上帝。虽孔子必予鲁矣。然则坛宫祀 先帝。而不祀方明。乃所以善为古礼也。或又谓古之帝王在祀典者。或庙焉。或坛焉。 先帝古之先王也。今为坛则宜仿古帝王坛。不宜仿坛宫为也。夫祀之礼。墠不如坛。坛不如祧。祧不如庙。当周之时。为二王封其子孙。设其庙祧。惟五帝。各以其德。配食于郊坛之兆。周官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之谓也。而坛制不见于经。唐书称古帝王坛高三尺方三丈五尺。非先王之制本然也。且吾闻之。天子崩而四海之内称之曰先王。宗庙亡而百世之后称之曰古帝
摈。传摈者。觐天子也。言传摈而不及方明者。诸侯不敢祀方明也。经曰。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拜日者。已觐诸侯而朝于日也。祀方明者。告于天地四方也。古者。天子觐诸侯。然后拜日。拜日然后祀方明。故曰。祀方明。天子之礼也。非诸侯之礼也。昔鲁公郊祀上帝。又象明堂。作太庙。禘祀文王。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周公之道衰。而鲁始郊禘。然而天下之情无穷。而先王之礼有时乎穷。礼穷则以义起之。以义起之。而能合于先王之意。则君子不以为滥也。使周室既亡之后。文王之庙不血食。而鲁公以旧诸侯祀文王。而不祀上帝。虽孔子必予鲁矣。然则坛宫祀 先帝。而不祀方明。乃所以善为古礼也。或又谓古之帝王在祀典者。或庙焉。或坛焉。 先帝古之先王也。今为坛则宜仿古帝王坛。不宜仿坛宫为也。夫祀之礼。墠不如坛。坛不如祧。祧不如庙。当周之时。为二王封其子孙。设其庙祧。惟五帝。各以其德。配食于郊坛之兆。周官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之谓也。而坛制不见于经。唐书称古帝王坛高三尺方三丈五尺。非先王之制本然也。且吾闻之。天子崩而四海之内称之曰先王。宗庙亡而百世之后称之曰古帝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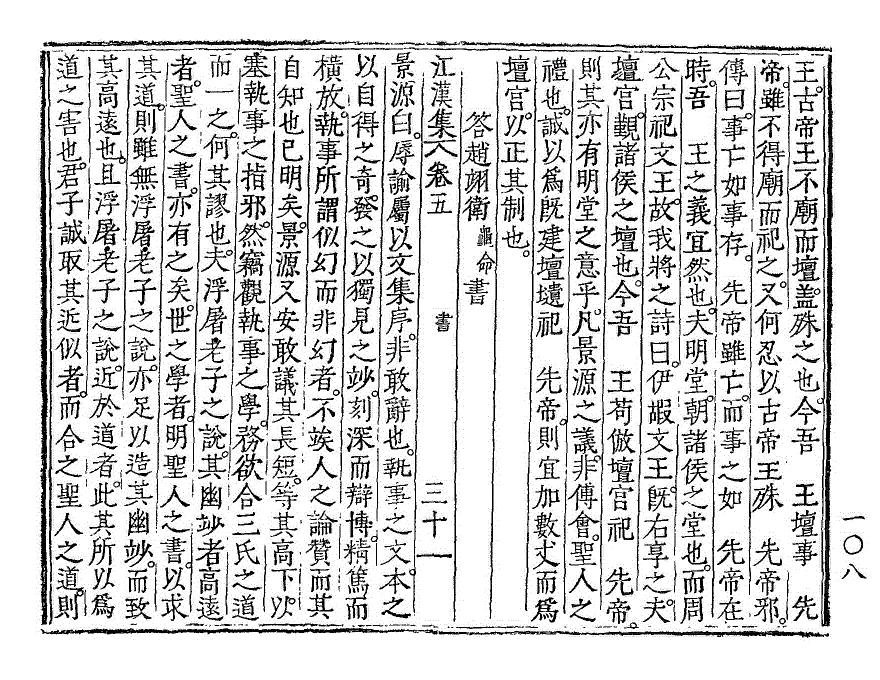 王。古帝王不庙而坛。盖殊之也。今吾 王坛事 先帝。虽不得庙而祀之。又何忍以古帝王殊 先帝邪。传曰。事亡如事存。 先帝虽亡。而事之如 先帝在时。吾 王之义宜然也。夫明堂。朝诸侯之堂也。而周公宗祀文王。故我将之诗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夫坛宫。觐诸侯之坛也。今吾 王苟仿坛宫祀 先帝。则其亦有明堂之意乎。凡景源之议。非傅会。圣人之礼也。诚以为既建坛壝祀 先帝。则宜加数丈而为坛宫。以正其制也。
王。古帝王不庙而坛。盖殊之也。今吾 王坛事 先帝。虽不得庙而祀之。又何忍以古帝王殊 先帝邪。传曰。事亡如事存。 先帝虽亡。而事之如 先帝在时。吾 王之义宜然也。夫明堂。朝诸侯之堂也。而周公宗祀文王。故我将之诗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夫坛宫。觐诸侯之坛也。今吾 王苟仿坛宫祀 先帝。则其亦有明堂之意乎。凡景源之议。非傅会。圣人之礼也。诚以为既建坛壝祀 先帝。则宜加数丈而为坛宫。以正其制也。答赵翊卫(龟命)书
景源白。辱谕属以文集序。非敢辞也。执事之文。本之以自得之奇。发之以独见之妙。刻深而辩博。精笃而横放。执事所谓似幻而非幻者。不俟人之论赞而其自知也已明矣。景源又安敢议其长短。等其高下。以塞执事之指邪。然窃观执事之学。务欲合三氏之道而一之。何其谬也。夫浮屠,老子之说。其幽妙者高远者。圣人之书。亦有之矣。世之学者。明圣人之书。以求其道。则虽无浮屠,老子之说。亦足以造其幽妙。而致其高远也。且浮屠,老子之说。近于道者。此其所以为道之害也。君子诚取其近似者。而合之圣人之道。则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9H 页
 其为害也益甚矣。杨氏之道。过于为我。墨氏之道。过于兼爱。子莫执杨墨之中。为我焉而非无君也。兼爱焉而非无父也。然而孟子非之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今执事执浮屠老子孔氏之中。虽空寂矣。未尝为浮屠之学。虽清静矣。未尝为老子之学。虽孝谨矣。未尝为孔氏之学。其害于圣人之道也。岂少哉。且浮屠不能为孔氏。孔氏不能为老子。其术异也。其术异而彊与之合者。惑也。今有人被袈裟。袈裟之上。加羽衣。羽衣之上。加深衣黄冠。而锡杖佩玉之声锵如也。则执事必知其怪焉。然而其所自以为学也。华严之文。道德之文。与诗书六艺之文。并陈于前。而交诵于口曰。我非浮屠之徒也。非老子之徒也。非孔氏之徒也。合浮屠老子孔氏之道而一之者也。呜呼。其亦杂矣。吾未见其能一也。然古之道术未始不合而为一。今之道术。二之而为老子。三之而为浮屠。有大人者。诚削其二之三之者而复一之。则天下无异学矣。今执事欲合三氏之道。其志诚大。而其虑诚远矣。然执事将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邪。将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邪。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则其不伤仁毁义。自陷于异端之学也几
其为害也益甚矣。杨氏之道。过于为我。墨氏之道。过于兼爱。子莫执杨墨之中。为我焉而非无君也。兼爱焉而非无父也。然而孟子非之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今执事执浮屠老子孔氏之中。虽空寂矣。未尝为浮屠之学。虽清静矣。未尝为老子之学。虽孝谨矣。未尝为孔氏之学。其害于圣人之道也。岂少哉。且浮屠不能为孔氏。孔氏不能为老子。其术异也。其术异而彊与之合者。惑也。今有人被袈裟。袈裟之上。加羽衣。羽衣之上。加深衣黄冠。而锡杖佩玉之声锵如也。则执事必知其怪焉。然而其所自以为学也。华严之文。道德之文。与诗书六艺之文。并陈于前。而交诵于口曰。我非浮屠之徒也。非老子之徒也。非孔氏之徒也。合浮屠老子孔氏之道而一之者也。呜呼。其亦杂矣。吾未见其能一也。然古之道术未始不合而为一。今之道术。二之而为老子。三之而为浮屠。有大人者。诚削其二之三之者而复一之。则天下无异学矣。今执事欲合三氏之道。其志诚大。而其虑诚远矣。然执事将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邪。将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邪。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则其不伤仁毁义。自陷于异端之学也几江汉集卷之五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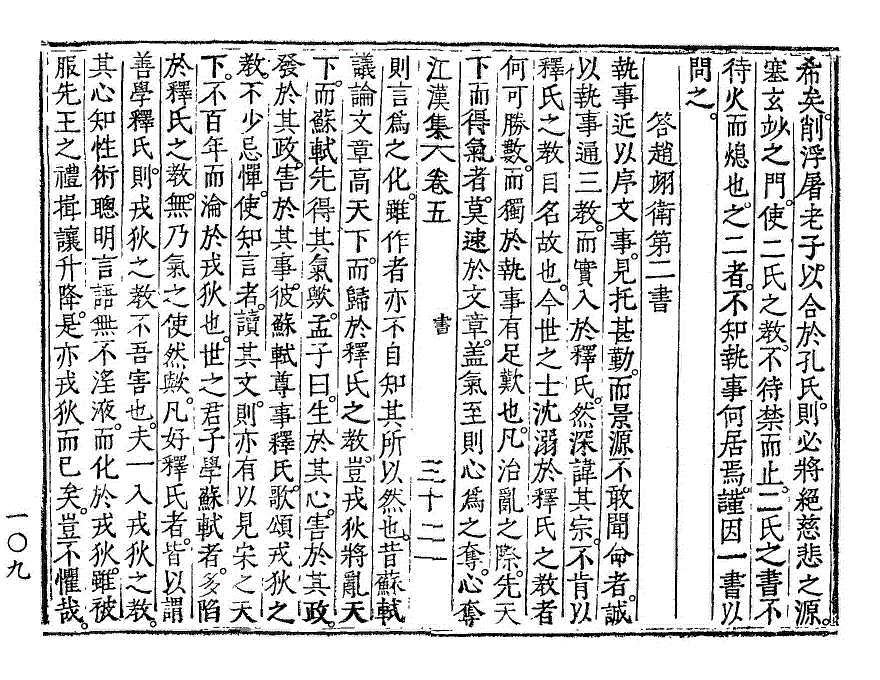 希矣。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则必将绝慈悲之源。塞玄妙之门。使二氏之教。不待禁而止。二氏之书不待火而熄也。之二者。不知执事何居焉。谨因一书以问之。
希矣。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则必将绝慈悲之源。塞玄妙之门。使二氏之教。不待禁而止。二氏之书不待火而熄也。之二者。不知执事何居焉。谨因一书以问之。答赵翊卫[第二书]
执事近以序文事。见托甚勤。而景源不敢闻命者。诚以执事通三教。而实入于释氏。然深讳其宗。不肯以释氏之教目名故也。今世之士沈溺于释氏之教者何可胜数。而独于执事有足叹也。凡治乱之际。先天下而得气者。莫速于文章。盖气至则心为之夺。心夺则言为之化。虽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昔苏轼议论文章高天下。而归于释氏之教。岂戎狄将乱天下。而苏轼先得其气欤。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彼苏轼尊事释氏。歌颂戎狄之教。不少忌惮。使知言者。读其文。则亦有以见宋之天下。不百年而沦于戎狄也。世之君子学苏轼者。多陷于释氏之教。无乃气之使然欤。凡好释氏者。皆以谓善学释氏。则戎狄之教不吾害也。夫一入戎狄之教。其心知性术聪明言语无不淫液。而化于戎狄。虽被服先王之礼揖让升降。是亦戎狄而已矣。岂不惧哉。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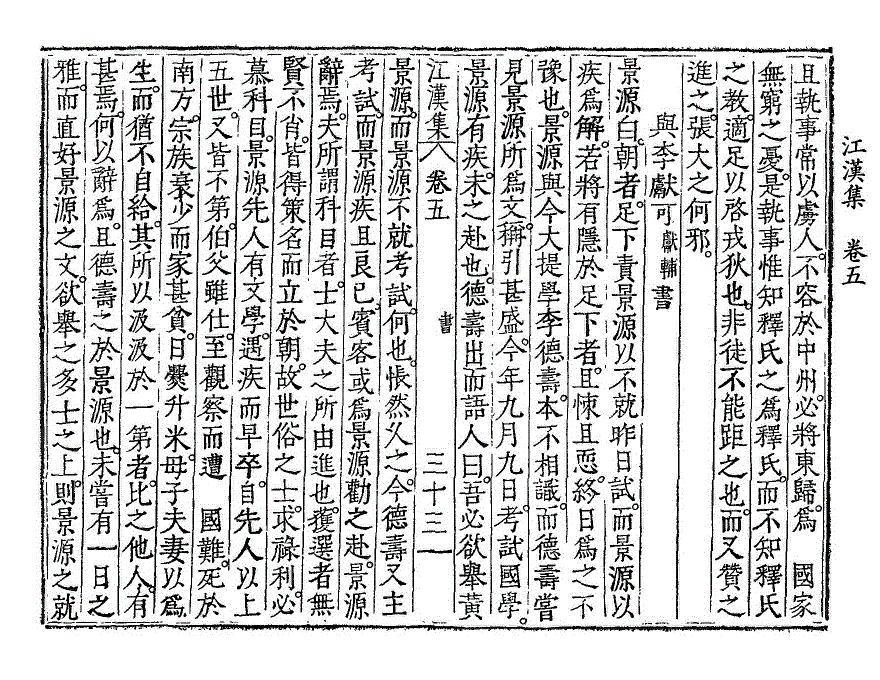 且执事常以虏人。不容于中州。必将东归。为 国家无穷之忧。是执事惟知释氏之为释氏。而不知释氏之教。适足以启戎狄也。非徒不能距之也。而又赞之进之。张大之何邪。
且执事常以虏人。不容于中州。必将东归。为 国家无穷之忧。是执事惟知释氏之为释氏。而不知释氏之教。适足以启戎狄也。非徒不能距之也。而又赞之进之。张大之何邪。与李献可(献辅)书
景源白。朝者。足下责景源以不就昨日试。而景源以疾为解。若将有隐于足下者。且悚且恧。终日为之不豫也。景源与今大提学李德寿。本不相识。而德寿尝见景源所为文。称引甚盛。今年九月九日。考试国学。景源有疾。未之赴也。德寿出而语人曰。吾必欲举黄景源。而景源不就考试。何也。怅然久之。今德寿又主考试。而景源疾且良已。宾客或为景源劝之赴。景源辞焉。夫所谓科目者。士大夫之所由进也。获选者无贤不肖。皆得策名而立于朝。故世俗之士。求禄利。必慕科目。景源先人有文学。遇疾而早卒。自先人以上五世。又皆不第。伯父虽仕。至观察而遭 国难。死于南方。宗族衰少而家甚贫。日爨升米。母子夫妻以为生。而犹不自给。其所以汲汲于一第者。比之他人。有甚焉。何以辞为。且德寿之于景源也。未尝有一日之雅。而直好景源之文。欲举之多士之上。则景源之就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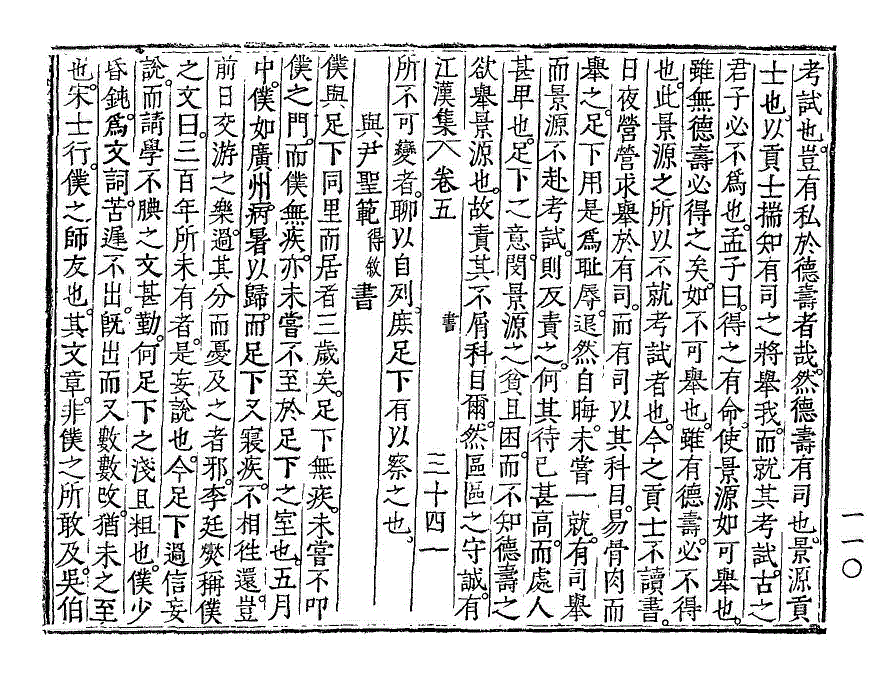 考试也。岂有私于德寿者哉。然德寿有司也。景源贡士也。以贡士揣知有司之将举我。而就其考试。古之君子必不为也。孟子曰。得之有命。使景源如可举也。虽无德寿必得之矣。如不可举也。虽有德寿。必不得也。此景源之所以不就考试者也。今之贡士不读书。日夜营营求举于有司。而有司以其科目。易骨肉而举之。足下用是为耻辱。退然自晦。未尝一就。有司举而景源不赴考试。则反责之。何其待己甚高。而处人甚卑也。足下之意。闵景源之贫且困。而不知德寿之欲举景源也。故责其不屑科目尔。然区区之守诚。有所不可变者。聊以自列。庶足下有以察之也。
考试也。岂有私于德寿者哉。然德寿有司也。景源贡士也。以贡士揣知有司之将举我。而就其考试。古之君子必不为也。孟子曰。得之有命。使景源如可举也。虽无德寿必得之矣。如不可举也。虽有德寿。必不得也。此景源之所以不就考试者也。今之贡士不读书。日夜营营求举于有司。而有司以其科目。易骨肉而举之。足下用是为耻辱。退然自晦。未尝一就。有司举而景源不赴考试。则反责之。何其待己甚高。而处人甚卑也。足下之意。闵景源之贫且困。而不知德寿之欲举景源也。故责其不屑科目尔。然区区之守诚。有所不可变者。聊以自列。庶足下有以察之也。与尹圣范(得叙)书
仆与足下同里而居者三岁矣。足下无疾。未尝不叩仆之门。而仆无疾。亦未尝不至于足下之室也。五月中。仆如广州。病暑以归。而足下又寝疾。不相往还。岂前日交游之乐。过其分而忧及之者邪。李廷燮称仆之文曰。三百年所未有者。是妄说也。今足下过信妄说。而请学不腆之文甚勤。何足下之浅且粗也。仆少昏钝。为文词。苦迟不出。既出而又数数改。犹未之至也。宋士行。仆之师友也。其文章。非仆之所敢及。吴伯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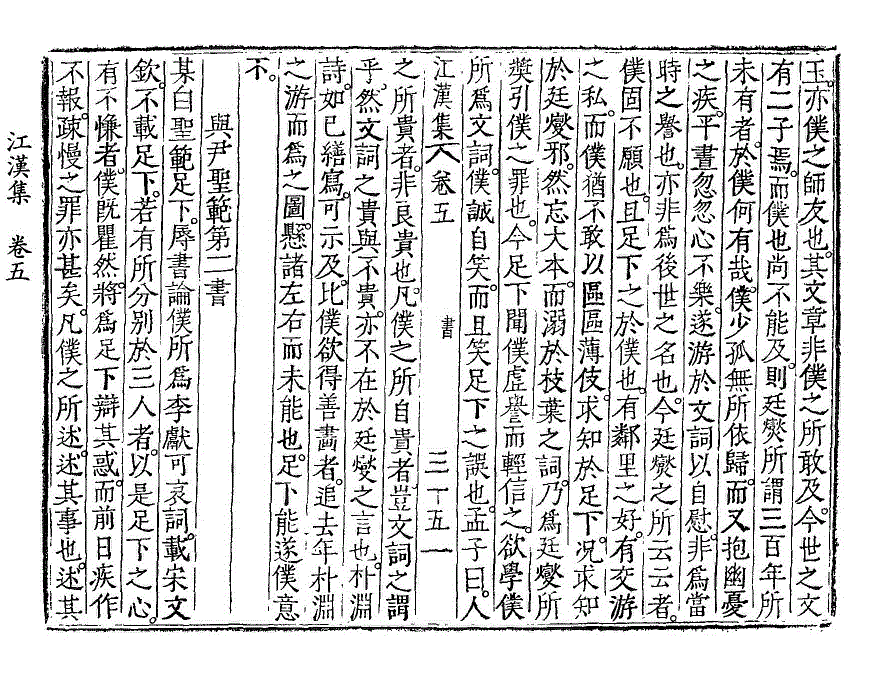 玉。亦仆之师友也。其文章非仆之所敢及。今世之文有二子焉。而仆也尚不能及。则廷燮所谓三百年所未有者。于仆何有哉。仆少孤无所依归。而又抱幽忧之疾。平昼忽忽心不乐。遂游于文词以自慰。非为当时之誉也。亦非为后世之名也。今廷燮之所云云者。仆固不愿也。且足下之于仆也。有邻里之好。有交游之私。而仆犹不敢以区区薄伎。求知于足下。况求知于廷燮邪。然忘大本。而溺于枝叶之词。乃为廷燮所奖引仆之罪也。今足下闻仆虚誉而轻信之。欲学仆所为文词。仆诚自笑。而且笑足下之误也。孟子曰。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凡仆之所自贵者。岂文词之谓乎。然文词之贵与不贵。亦不在于廷燮之言也。朴渊诗。如已缮写。可示及。比仆欲得善画者。追去年朴渊之游而为之图。悬诸左右而未能也。足下能遂仆意不。
玉。亦仆之师友也。其文章非仆之所敢及。今世之文有二子焉。而仆也尚不能及。则廷燮所谓三百年所未有者。于仆何有哉。仆少孤无所依归。而又抱幽忧之疾。平昼忽忽心不乐。遂游于文词以自慰。非为当时之誉也。亦非为后世之名也。今廷燮之所云云者。仆固不愿也。且足下之于仆也。有邻里之好。有交游之私。而仆犹不敢以区区薄伎。求知于足下。况求知于廷燮邪。然忘大本。而溺于枝叶之词。乃为廷燮所奖引仆之罪也。今足下闻仆虚誉而轻信之。欲学仆所为文词。仆诚自笑。而且笑足下之误也。孟子曰。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凡仆之所自贵者。岂文词之谓乎。然文词之贵与不贵。亦不在于廷燮之言也。朴渊诗。如已缮写。可示及。比仆欲得善画者。追去年朴渊之游而为之图。悬诸左右而未能也。足下能遂仆意不。与尹圣范[第二书]
某白圣范足下。辱书论仆所为李献可哀词。载宋文钦。不载足下。若有所分别于三人者。以是足下之心。有不慊者。仆既瞿然。将为足下辩其惑。而前日疾作不报。疏慢之罪亦甚矣。凡仆之所述。述其事也。述其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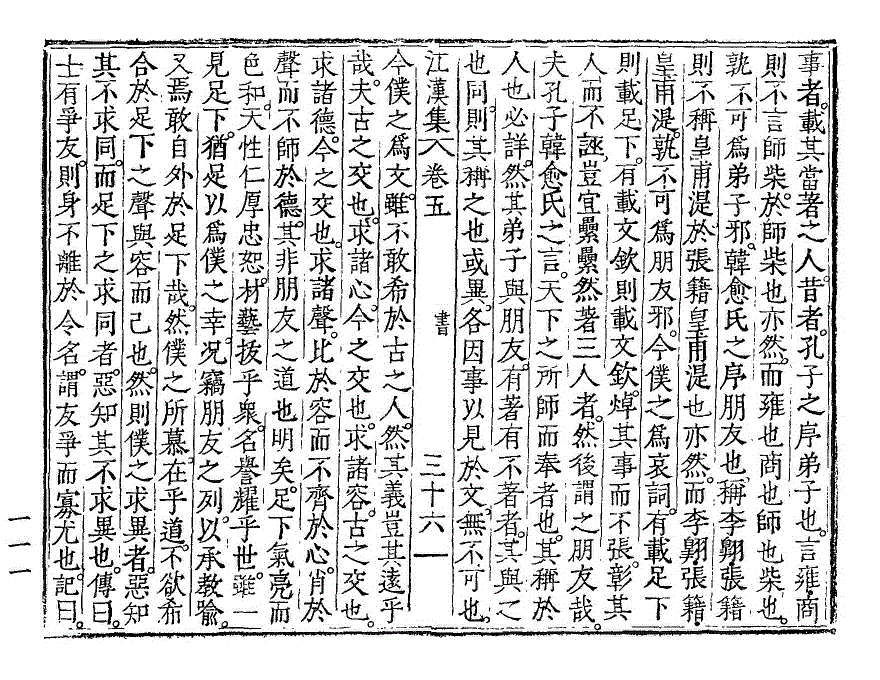 事者。载其当著之人。昔者。孔子之序弟子也。言雍,商则不言师柴。于师柴也亦然。而雍也商也师也柴也。孰不可为弟子邪。韩愈氏之序朋友也。称李翱,张籍则不称皇甫湜。于张籍皇甫湜也亦然。而李翱,张籍,皇甫湜。孰不可为朋友邪。今仆之为哀词。有载足下则载足下。有载文钦则载文钦。焯其事而不张。彰其人而不诬。岂宜累累然著三人者。然后谓之朋友哉。夫孔子韩愈氏之言。天下之所师而奉者也。其称于人也必详。然其弟子与朋友。有著有不著者。其与之也同。则其称之也或异。各因事以见于文。无不可也。今仆之为文。虽不敢希于古之人。然其义岂其远乎哉。夫古之交也。求诸心。今之交也。求诸容。古之交也。求诸德。今之交也。求诸声。比于容而不齐于心。肖于声而不师于德。其非朋友之道也明矣。足下气亮而色和。天性仁厚忠恕。材艺拔乎众。名誉耀乎世。虽一见足下。犹足以为仆之幸。况窃朋友之列。以承教喻。又焉敢自外于足下哉。然仆之所慕。在乎道。不欲希合于足下之声与容而已也。然则仆之求异者。恶知其不求同。而足下之求同者。恶知其不求异也。传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谓友争而寡尤也。记曰。
事者。载其当著之人。昔者。孔子之序弟子也。言雍,商则不言师柴。于师柴也亦然。而雍也商也师也柴也。孰不可为弟子邪。韩愈氏之序朋友也。称李翱,张籍则不称皇甫湜。于张籍皇甫湜也亦然。而李翱,张籍,皇甫湜。孰不可为朋友邪。今仆之为哀词。有载足下则载足下。有载文钦则载文钦。焯其事而不张。彰其人而不诬。岂宜累累然著三人者。然后谓之朋友哉。夫孔子韩愈氏之言。天下之所师而奉者也。其称于人也必详。然其弟子与朋友。有著有不著者。其与之也同。则其称之也或异。各因事以见于文。无不可也。今仆之为文。虽不敢希于古之人。然其义岂其远乎哉。夫古之交也。求诸心。今之交也。求诸容。古之交也。求诸德。今之交也。求诸声。比于容而不齐于心。肖于声而不师于德。其非朋友之道也明矣。足下气亮而色和。天性仁厚忠恕。材艺拔乎众。名誉耀乎世。虽一见足下。犹足以为仆之幸。况窃朋友之列。以承教喻。又焉敢自外于足下哉。然仆之所慕。在乎道。不欲希合于足下之声与容而已也。然则仆之求异者。恶知其不求同。而足下之求同者。恶知其不求异也。传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谓友争而寡尤也。记曰。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2H 页
 燕朋逆其师。谓朋之燕昵而违于道也。足下之贤。固非仆之所能及。而既以古人之道。相处焉。请与足下为争友。而毋为燕朋。使后世知三人者。其道不相异。卓然有成。则不负于献可。
燕朋逆其师。谓朋之燕昵而违于道也。足下之贤。固非仆之所能及。而既以古人之道。相处焉。请与足下为争友。而毋为燕朋。使后世知三人者。其道不相异。卓然有成。则不负于献可。与李士固(思重)书
景源白。湖中幽旷。而又有田园之乐。士固閒居。穷道艺治诗书。徜徉乎木石之间。何其守己之静而求志之笃也。前书论置长史司以遵 明制者。非以 明制为尽善也。 王国之礼当然也。而说者曰。三十九员。不足以具百官之列。夫王国之官。有命于天子者。有不命于天子者。命于天子者。固有常数。而不命于天子者。虽无常数。亦不革也。周官曰。陈其殷。置其辅。殷也者。适士之谓也。辅也者。庶士之谓也。盖三代诸侯之国。自适士以上。凡三十五人。命于天子。而自庶士以下。不命于天子。然置庶士而不置适士。则无以正百官之名也。置适士而不置庶士。则亦无以备百官之数也。今 王家欲遵 明制。则自长史以下三十九员。宜本其名而正其职。如 天子之所命者。至于众官。虽不与于是数。亦存之。如不命于 天子者可也。赠序蒙见属。而比苦颈疾。不能沉思为文字。俟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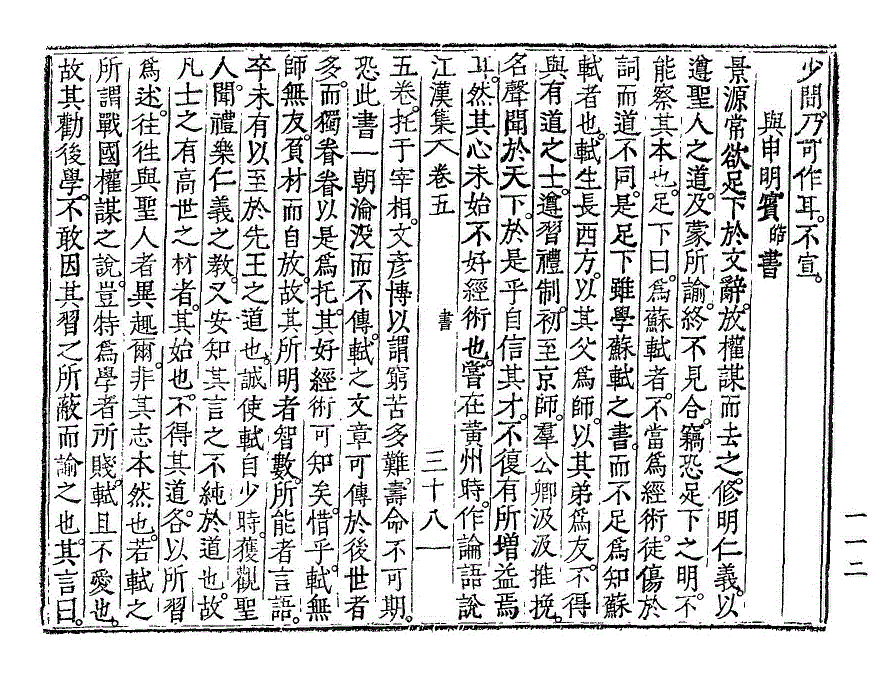 少间。乃可作耳。不宣。
少间。乃可作耳。不宣。与申明宾(皓)书
景源常欲足下于文辞。放权谋而去之。修明仁义。以遵圣人之道。及蒙所谕。终不见合。窃恐足下之明。不能察其本也。足下曰。为苏轼者。不当为经术。徒伤于词而道不同。是足下虽学苏轼之书。而不足为知苏轼者也。轼生长西方。以其父为师。以其弟为友。不得与有道之士。遵习礼制。初至京师。群公卿汲汲推挽。名声闻于天下。于是乎自信其才。不复有所增益焉耳。然其心未始不好经术也。尝在黄州时。作论语说五卷。托于宰相。文彦博以谓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朝沦没而不传。轼之文章可传于后世者多。而独眷眷以是为托。其好经术可知矣。惜乎。轼无师无友。负材而自放。故其所明者智数。所能者言语。卒未有以至于先王之道也。诚使轼自少时。获观圣人。闻礼乐仁义之教。又安知其言之不纯于道也。故凡士之有高世之材者。其始也。不得其道。各以所习为述。往往与圣人者异趣尔。非其志本然也。若轼之所谓战国权谋之说。岂特为学者所贱。轼且不爱也。故其劝后学。不敢因其习之所蔽而谕之也。其言曰。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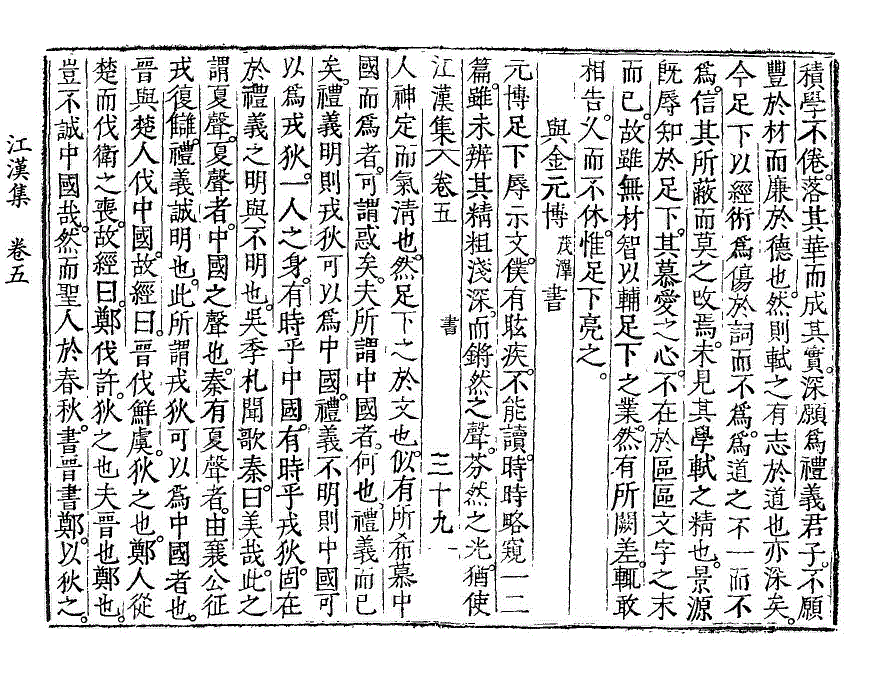 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为礼义君子。不愿丰于材而廉于德也。然则轼之有志于道也亦深矣。今足下以经术为伤于词而不为。为道之不一而不为。信其所蔽而莫之改焉。未见其学轼之精也。景源既辱知于足下。其慕爱之心。不在于区区文字之末而已。故虽无材智以辅足下之业。然有所阙差。辄敢相告。久而不休。惟足下亮之。
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为礼义君子。不愿丰于材而廉于德也。然则轼之有志于道也亦深矣。今足下以经术为伤于词而不为。为道之不一而不为。信其所蔽而莫之改焉。未见其学轼之精也。景源既辱知于足下。其慕爱之心。不在于区区文字之末而已。故虽无材智以辅足下之业。然有所阙差。辄敢相告。久而不休。惟足下亮之。与金元博(茂泽)书
元博足下辱示文。仆有眩疾。不能读。时时略窥一二篇。虽未辨其精粗浅深。而锵然之声。芬然之光。犹使人神定而气清也。然足下之于文也。似有所希慕中国而为者。可谓惑矣。夫所谓中国者。何也。礼义而已矣。礼义明则戎狄可以为中国。礼义不明则中国可以为戎狄。一人之身。有时乎中国。有时乎戎狄。固在于礼义之明与不明也。吴季札闻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夏声者。中国之声也。秦有夏声者。由襄公征戎复雠。礼义诚明也。此所谓戎狄可以为中国者也。晋与楚人伐中国。故经曰。晋伐鲜虞。狄之也。郑人从楚而伐卫之丧。故经曰。郑伐许。狄之也夫晋也郑也。岂不诚中国哉。然而圣人于春秋。书晋书郑。以狄之。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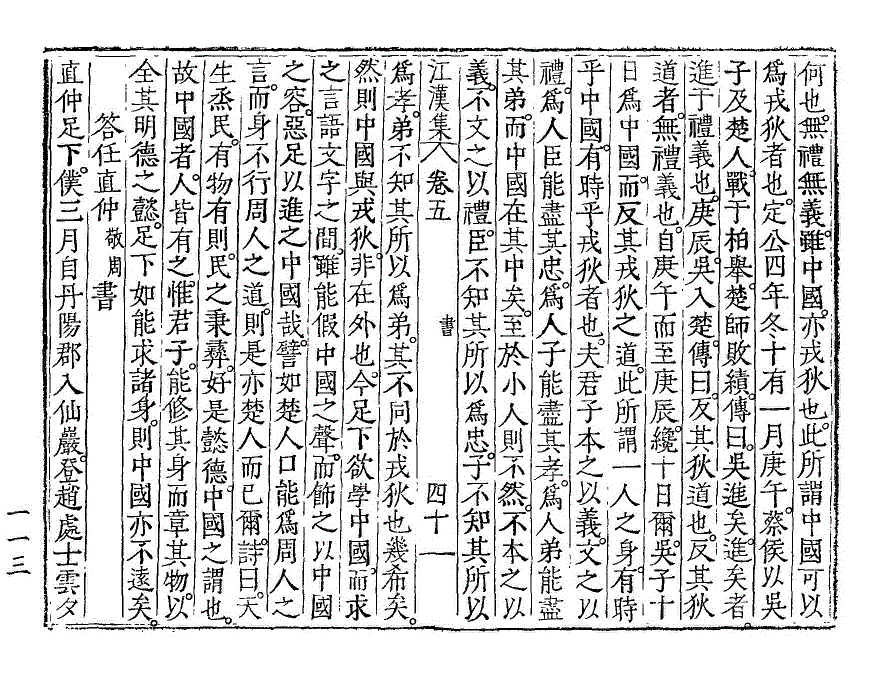 何也。无礼无义。虽中国。亦戎狄也。此所谓中国可以为戎狄者也。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传曰。吴进矣。进矣者。进于礼义也。庚辰。吴入楚。传曰。反其狄道也。反其狄道者。无礼义也。自庚午而至庚辰。才十日尔。吴子十日为中国。而反其戎狄之道。此所谓一人之身。有时乎中国。有时乎戎狄者也。夫君子本之以义。文之以礼。为人臣能尽其忠。为人子能尽其孝。为人弟能尽其弟。而中国在其中矣。至于小人则不然。不本之以义。不文之以礼。臣不知其所以为忠。子不知其所以为孝。弟不知其所以为弟。其不同于戎狄也几希矣。然则中国与戎狄。非在外也。今足下欲学中国。而求之言语文字之间。虽能假中国之声。而饰之以中国之容。恶足以进之中国哉。譬如楚人口能为周人之言。而身不行周人之道。则是亦楚人而已尔。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国之谓也。故中国者。人皆有之。惟君子。能修其身而章其物。以全其明德之懿。足下如能求诸身。则中国亦不远矣。
何也。无礼无义。虽中国。亦戎狄也。此所谓中国可以为戎狄者也。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传曰。吴进矣。进矣者。进于礼义也。庚辰。吴入楚。传曰。反其狄道也。反其狄道者。无礼义也。自庚午而至庚辰。才十日尔。吴子十日为中国。而反其戎狄之道。此所谓一人之身。有时乎中国。有时乎戎狄者也。夫君子本之以义。文之以礼。为人臣能尽其忠。为人子能尽其孝。为人弟能尽其弟。而中国在其中矣。至于小人则不然。不本之以义。不文之以礼。臣不知其所以为忠。子不知其所以为孝。弟不知其所以为弟。其不同于戎狄也几希矣。然则中国与戎狄。非在外也。今足下欲学中国。而求之言语文字之间。虽能假中国之声。而饰之以中国之容。恶足以进之中国哉。譬如楚人口能为周人之言。而身不行周人之道。则是亦楚人而已尔。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国之谓也。故中国者。人皆有之。惟君子。能修其身而章其物。以全其明德之懿。足下如能求诸身。则中国亦不远矣。答任直仲(敬周)书
直仲足下。仆三月自丹阳郡入仙岩。登赵处士云夕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4H 页
 亭。与吴伯玉。临澄潭。围棋不返。故太学虽有考试。而未之赴焉。彼世俗讥骂之言。何足恤哉。辱惠书。论召穆公为周三公。不能救厉王之祸。共和时。摄天子事。及王崩。拥立太子。平淮夷。而江汉。犹书其名以刺之。甚不然也。始厉王用荣夷公为卿士。又得卫巫以监谤。贼杀言者。穆公谏曰。为川者。决之使道。为民者。宣之使言。塞下之口。遂上之过。恐为社稷之忧。厉王不听。虐益甚。诸侯皆叛。故穆公作诗以讽。民劳是也。王不用穆公之谏。卒亡天下。言诗者。孰谓江汉刺穆公也。共和时。上无天子凡十四年。大臣行政。以摄天子之事。而穆公能全臣节。及厉王既崩。然后立太子。周道复兴。则江汉。美穆公也。非刺穆公也。诚使穆公。立太子于厉王在彘之时。则必知其无共和矣。然厉王未释天位。而大臣又立太子。是中国有二天子也。其可乎。江汉五章。称康公以为召祖。至于穆公则名之。所以别于康公也。若康公不见于诗。则穆公不当书名。故崧高曰。王命召伯。召伯者。穆公也。夫常武。不名程伯。六月。不名尹吉甫。烝民。不名仲山甫。而江汉独名穆公。固可疑。然穆公如有大过。则非特江汉名之也。崧高。亦当名之也。名于江汉。而不名于崧高。安在
亭。与吴伯玉。临澄潭。围棋不返。故太学虽有考试。而未之赴焉。彼世俗讥骂之言。何足恤哉。辱惠书。论召穆公为周三公。不能救厉王之祸。共和时。摄天子事。及王崩。拥立太子。平淮夷。而江汉。犹书其名以刺之。甚不然也。始厉王用荣夷公为卿士。又得卫巫以监谤。贼杀言者。穆公谏曰。为川者。决之使道。为民者。宣之使言。塞下之口。遂上之过。恐为社稷之忧。厉王不听。虐益甚。诸侯皆叛。故穆公作诗以讽。民劳是也。王不用穆公之谏。卒亡天下。言诗者。孰谓江汉刺穆公也。共和时。上无天子凡十四年。大臣行政。以摄天子之事。而穆公能全臣节。及厉王既崩。然后立太子。周道复兴。则江汉。美穆公也。非刺穆公也。诚使穆公。立太子于厉王在彘之时。则必知其无共和矣。然厉王未释天位。而大臣又立太子。是中国有二天子也。其可乎。江汉五章。称康公以为召祖。至于穆公则名之。所以别于康公也。若康公不见于诗。则穆公不当书名。故崧高曰。王命召伯。召伯者。穆公也。夫常武。不名程伯。六月。不名尹吉甫。烝民。不名仲山甫。而江汉独名穆公。固可疑。然穆公如有大过。则非特江汉名之也。崧高。亦当名之也。名于江汉。而不名于崧高。安在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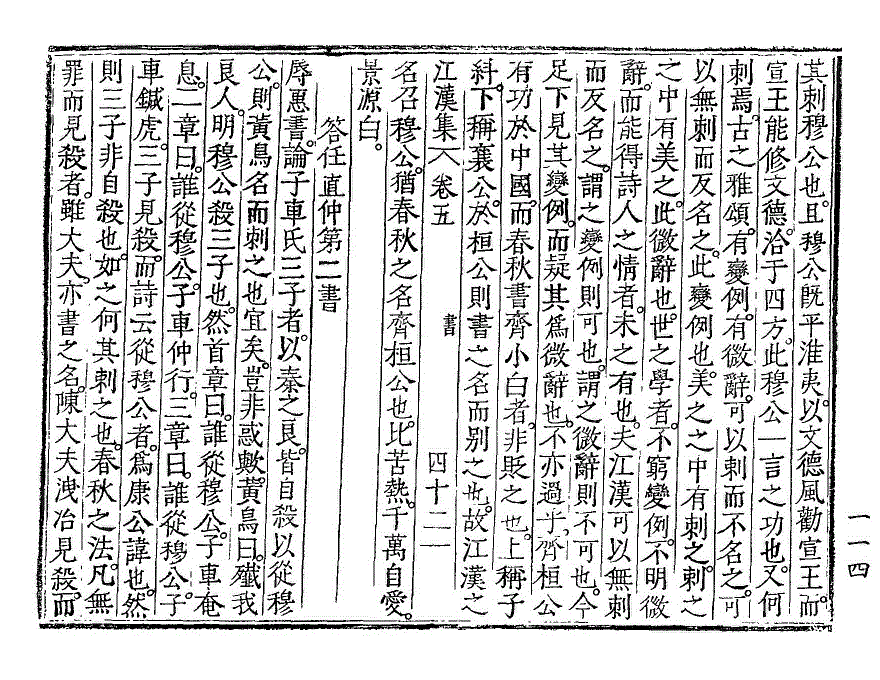 其刺穆公也。且穆公既平淮夷。以文德风劝宣王。而宣王能修文德。洽于四方。此穆公一言之功也。又何刺焉。古之雅颂。有变例。有微辞。可以刺而不名之。可以无刺而反名之。此变例也。美之之中有刺之。刺之之中有美之。此微辞也。世之学者。不穷变例。不明微辞。而能得诗人之情者。未之有也。夫江汉可以无刺而反名之。谓之变例则可也。谓之微辞则不可也。今足下见其变例。而疑其为微辞也。不亦过乎。齐桓公有功于中国。而春秋书齐小白者。非贬之也。上称子纠。下称襄公。于桓公则书之名而别之也。故江汉之名召穆公。犹春秋之名齐桓公也。比苦热。千万自爱。景源白。
其刺穆公也。且穆公既平淮夷。以文德风劝宣王。而宣王能修文德。洽于四方。此穆公一言之功也。又何刺焉。古之雅颂。有变例。有微辞。可以刺而不名之。可以无刺而反名之。此变例也。美之之中有刺之。刺之之中有美之。此微辞也。世之学者。不穷变例。不明微辞。而能得诗人之情者。未之有也。夫江汉可以无刺而反名之。谓之变例则可也。谓之微辞则不可也。今足下见其变例。而疑其为微辞也。不亦过乎。齐桓公有功于中国。而春秋书齐小白者。非贬之也。上称子纠。下称襄公。于桓公则书之名而别之也。故江汉之名召穆公。犹春秋之名齐桓公也。比苦热。千万自爱。景源白。答任直仲[第二书]
辱惠书。论子车氏三子者。以秦之良。皆自杀以从穆公。则黄鸟名而刺之也宜矣。岂非惑欤。黄鸟曰。歼我良人。明穆公杀三子也。然首章曰。谁从穆公。子车奄息。二章曰。谁从穆公。子车仲行。三章曰。谁从穆公。子车针虎。三子见杀。而诗云从穆公者。为康公讳也。然则三子非自杀也。如之何其刺之也。春秋之法。凡无罪而见杀者。虽大夫。亦书之名。陈大夫泄冶见杀。而
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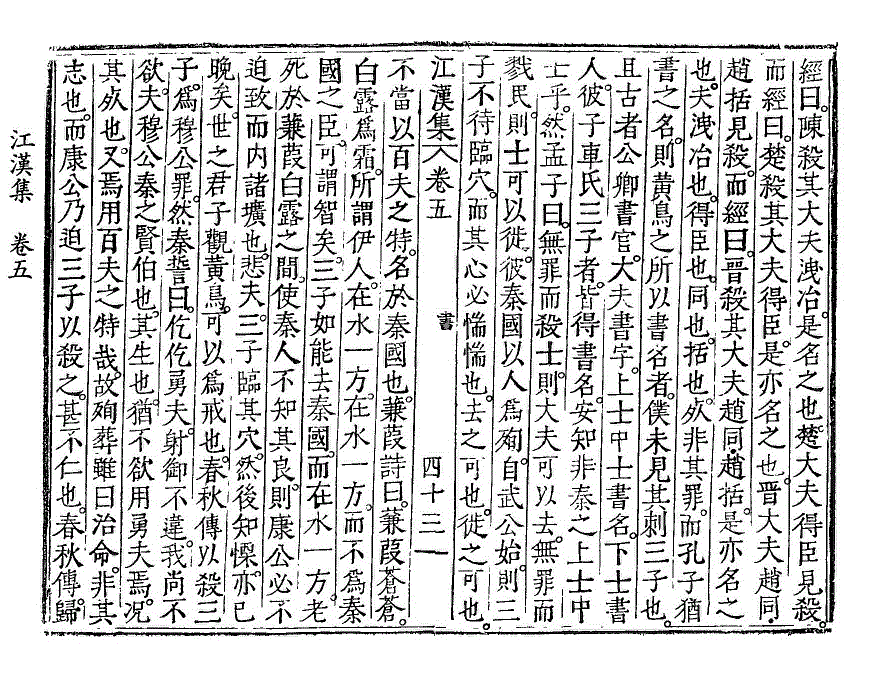 经曰。陈杀其大夫泄冶。是名之也。楚大夫得臣见杀。而经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是亦名之也。晋大夫赵同,赵括见杀。而经曰。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是亦名之也。夫泄冶也。得臣也。同也。括也。死非其罪。而孔子犹书之名。则黄鸟之所以书名者。仆未见其刺三子也。且古者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彼子车氏三子者。皆得书名。安知非秦之上士中士乎。然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彼秦国以人为殉。自武公始。则三子不待临穴。而其心必惴惴也。去之可也。徙之可也。不当以百夫之特。名于秦国也。蒹葭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而不为秦国之臣。可谓智矣。三子如能去秦国。而在水一方。老死于蒹葭白露之间。使秦人不知其良。则康公必不迫致而内诸圹也。悲夫。三子临其穴。然后知慄。亦已晚矣。世之君子观黄鸟。可以为戒也。春秋传以杀三子。为穆公罪。然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夫穆公秦之贤伯也。其生也。犹不欲用勇夫焉。况其死也。又焉用百夫之特哉。故殉葬虽曰治命。非其志也。而康公乃迫三子以杀之。甚不仁也。春秋传。归
经曰。陈杀其大夫泄冶。是名之也。楚大夫得臣见杀。而经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是亦名之也。晋大夫赵同,赵括见杀。而经曰。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是亦名之也。夫泄冶也。得臣也。同也。括也。死非其罪。而孔子犹书之名。则黄鸟之所以书名者。仆未见其刺三子也。且古者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彼子车氏三子者。皆得书名。安知非秦之上士中士乎。然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彼秦国以人为殉。自武公始。则三子不待临穴。而其心必惴惴也。去之可也。徙之可也。不当以百夫之特。名于秦国也。蒹葭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而不为秦国之臣。可谓智矣。三子如能去秦国。而在水一方。老死于蒹葭白露之间。使秦人不知其良。则康公必不迫致而内诸圹也。悲夫。三子临其穴。然后知慄。亦已晚矣。世之君子观黄鸟。可以为戒也。春秋传以杀三子。为穆公罪。然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夫穆公秦之贤伯也。其生也。犹不欲用勇夫焉。况其死也。又焉用百夫之特哉。故殉葬虽曰治命。非其志也。而康公乃迫三子以杀之。甚不仁也。春秋传。归江汉集卷之五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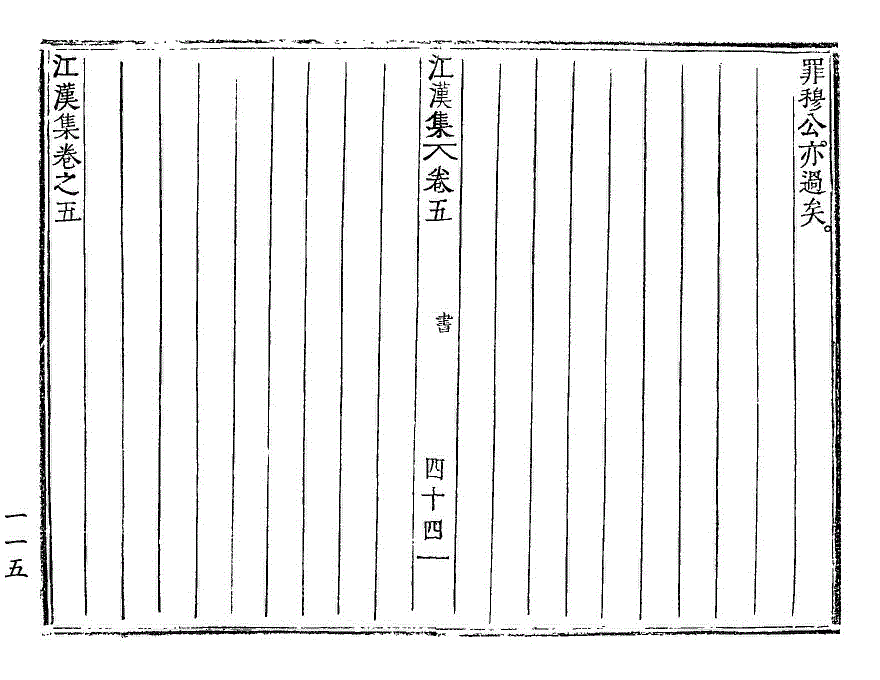 罪穆公。亦过矣。
罪穆公。亦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