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尊性录○复性篇
尊性录○复性篇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5H 页
 [穷理章]
[穷理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曰。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未至乎力行而为仁。然从事于此。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近思者。以类而推。
子思子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朱子曰。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穷理。无以真知至善之所在也。○程子曰。诚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而行之者也。故大学之序。先致知而后诚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无圣人之聪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践其行事之迹。则亦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也哉。惟其烛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乐循理尔。
(已上言穷理然后可以践履。)
按知行工夫。言其轻重。则行重于知。而语其先后。则知先于行。故上两段。先言穷理然后。可以践修之意。而穷理之中。自有用力之地。穷理又当积习然后。有豁然贯通之效。穷理又自有节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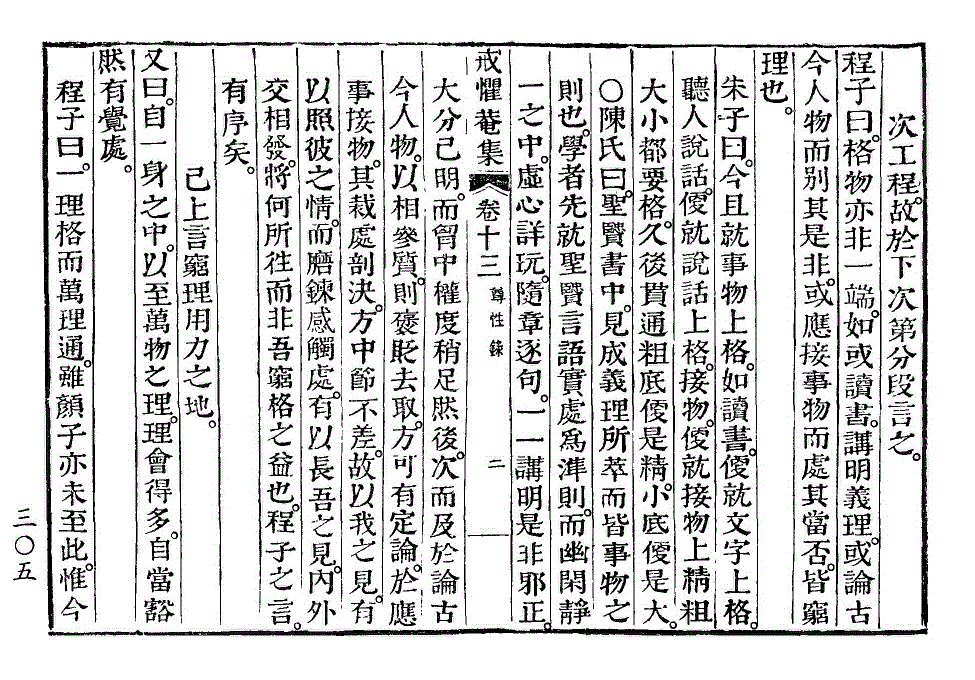 次工程。故于下次第分段言之。
次工程。故于下次第分段言之。程子曰。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
朱子曰。今且就事物上格。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后贯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陈氏曰。圣贤书中。见成义理所萃而皆事物之则也。学者先就圣贤言语实处为准则。而幽闲静一之中。虚心详玩。随章逐句。一一讲明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权度稍足然后。次而及于论古今人物。以相参质。则褒贬去取。方可有定论。于应事接物。其裁处剖决。方中节不差。故以我之见。有以照彼之情。而磨鍊感触处。有以长吾之见。内外交相发。将何所往而非吾穷格之益也。程子之言。有序矣。
(已上言穷理用力之地。)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觉处。
程子曰。一理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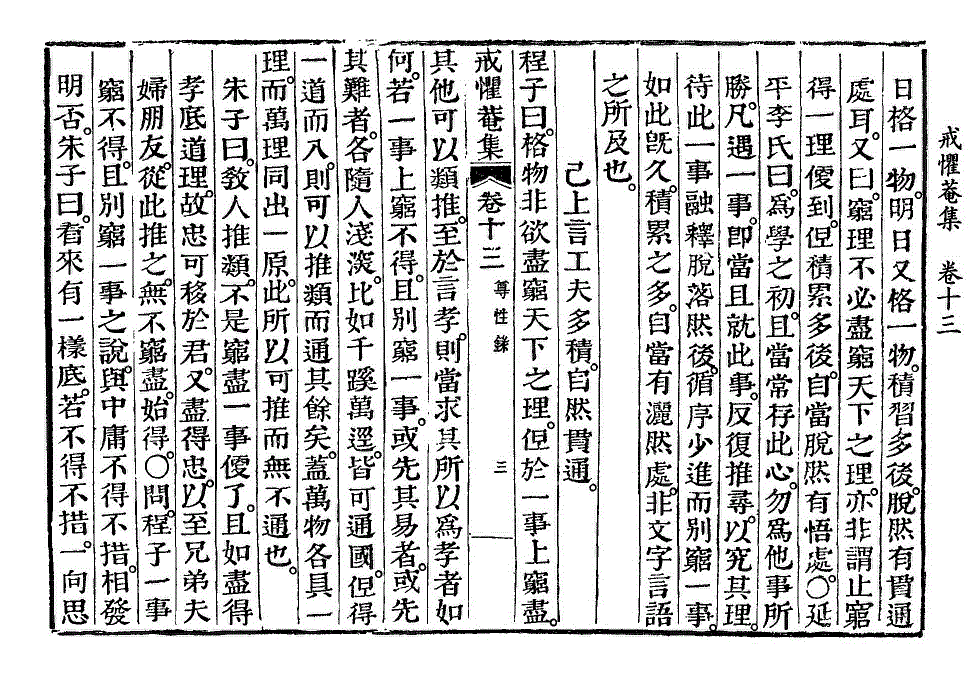 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多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又曰。穷理不必尽穷天下之理。亦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延平李氏曰。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
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多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又曰。穷理不必尽穷天下之理。亦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延平李氏曰。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已上言工夫多积。自然贯通。)
程子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比如千蹊万径。皆可通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馀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
朱子曰。教人推类。不是穷尽一事便了。且如尽得孝底道理。故忠可移于君。又尽得忠。以至兄弟夫妇朋友。从此推之。无不穷尽。始得。○问。程子一事穷不得。且别穷一事之说。与中庸不得不措。相发明否。朱子曰。看来有一样底。若不得不措。一向思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6L 页
 虑这个。少间担阁了。若谓穷一事不得。便掉了。别穷一事。又轻忽了。也不得。程子见学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说此话。又曰。理会不得。若专一守在这里。却昏了。须着别穷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又曰。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卒急难晓。只得姑放住。○问。千蹊万径。皆可通国。不知从一事上。便穷到一原处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类而推。理固是一理。须是把这个做样子。却从这里推去。始得。且如事亲。固当尽其事之之道。若得于亲是如何。不得于亲又当如何。以此推之于事君。知得于君是如何。不得于君又当如何。推以事长。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玉溪卢氏曰。一事穷尽。他可类推。此贯通觉悟之机也。如言孝则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此格物之要法。一事穷不得则穷一事。此格物之活法。
虑这个。少间担阁了。若谓穷一事不得。便掉了。别穷一事。又轻忽了。也不得。程子见学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说此话。又曰。理会不得。若专一守在这里。却昏了。须着别穷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又曰。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卒急难晓。只得姑放住。○问。千蹊万径。皆可通国。不知从一事上。便穷到一原处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类而推。理固是一理。须是把这个做样子。却从这里推去。始得。且如事亲。固当尽其事之之道。若得于亲是如何。不得于亲又当如何。以此推之于事君。知得于君是如何。不得于君又当如何。推以事长。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玉溪卢氏曰。一事穷尽。他可类推。此贯通觉悟之机也。如言孝则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此格物之要法。一事穷不得则穷一事。此格物之活法。又曰。物必有理。皆所当穷。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鬼神吾知其幽显而已矣。则是已然之辞。又何理之可穷哉。
又曰。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如何而为奉养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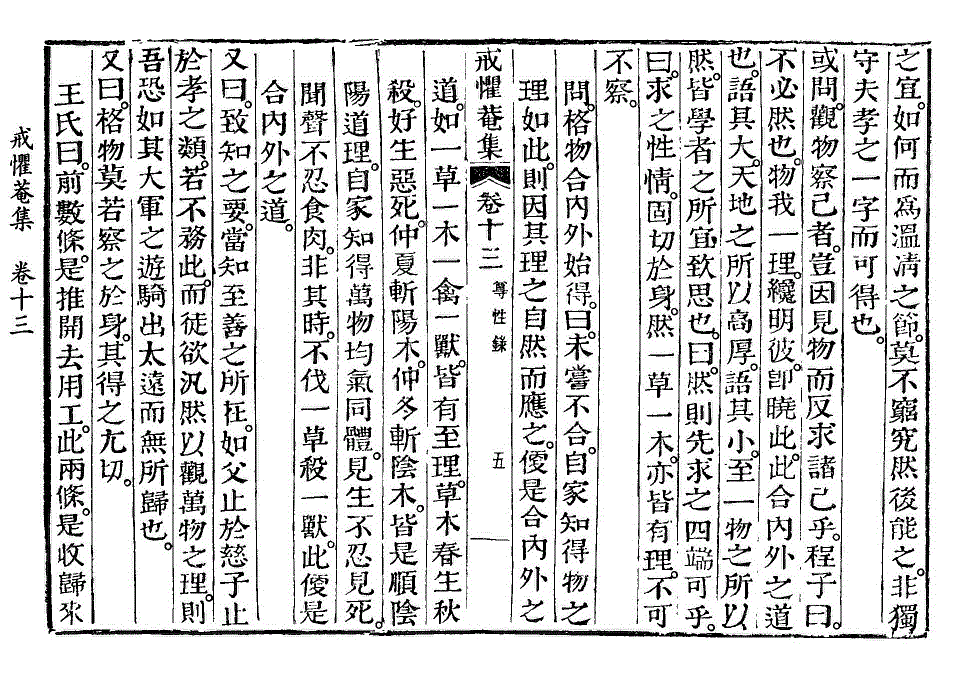 之宜。如何而为温凊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之宜。如何而为温凊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学者之所宜致思也。曰。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问。格物合内外始得。曰。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是合内外之道。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至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草杀一兽。此便是合内外之道。
又曰。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汎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如其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王氏曰。前数条。是推开去用工。此两条。是收归来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7L 页
 用工。
用工。(已上言穷理次第工程。)
按此以上。既历论穷理之道。而读书讲明义理。尤为穷理之要。故下段言读书之方。又以循序致精。要作实用为主。故于下次第言之。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程子曰。人之蕴蓄。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尹彦明问为学之方。程子曰。公要知为学。须是读书。将圣贤言语。玩味入心记着然后。力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当。古之圣贤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其馀则顺之者为君子。而可以为劝。背之者为小人。而可以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
(已上言穷理。不可不读书。)
朱子曰。读书。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间断而无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贪多务广。往往未启其端而遽已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8H 页
 欲探其终。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虽复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匆匆。常若有所奔趍迫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厌。以异于彼之怠忽间断哉。欲速不达。进锐退速。正谓此也。诚能鉴此。有以反以。则心潜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读之书。文理接续。血脉贯通。自然渐渍浃洽。心与理会。而善之为劝者深。恶之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为读书之法也。
欲探其终。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虽复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匆匆。常若有所奔趍迫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厌。以异于彼之怠忽间断哉。欲速不达。进锐退速。正谓此也。诚能鉴此。有以反以。则心潜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读之书。文理接续。血脉贯通。自然渐渍浃洽。心与理会。而善之为劝者深。恶之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为读书之法也。又曰。将合看文字。择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书。一日随力。且看一两段。一段已晓。方换一段。一书皆毕。方换一书。先要虚心平气。熟读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诸家注解。一一通贯然后。可以较其是非。以求圣贤立言之本意。虽已得之。亦更反复玩味。令其义理沦肌浃髓然后。乃可言学耳。尹和靖门人。赞其师曰。丕哉圣训。六经之篇。耳顺心得。如诵己言。至此地位。始是读书人耳。
又曰。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
程子曰。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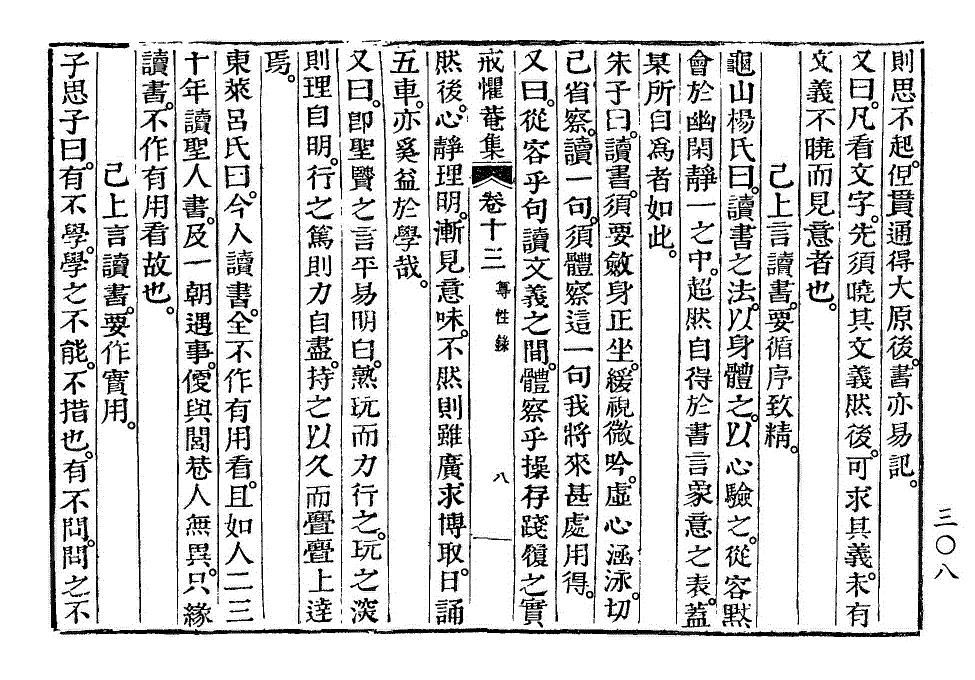 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
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又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义。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已上言读书。要循序致精。)
龟山杨氏曰。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朱子曰。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读一句。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
又曰。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察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又曰。即圣贤之言平易明白。熟玩而力行之。玩之深则理自明。行之笃则力自尽。持之以久而亹亹上达焉。
东莱吕氏曰。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朝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
(已上言读书。要作实用。)
子思子曰。有不学。学之不能。不措也。有不问。问之不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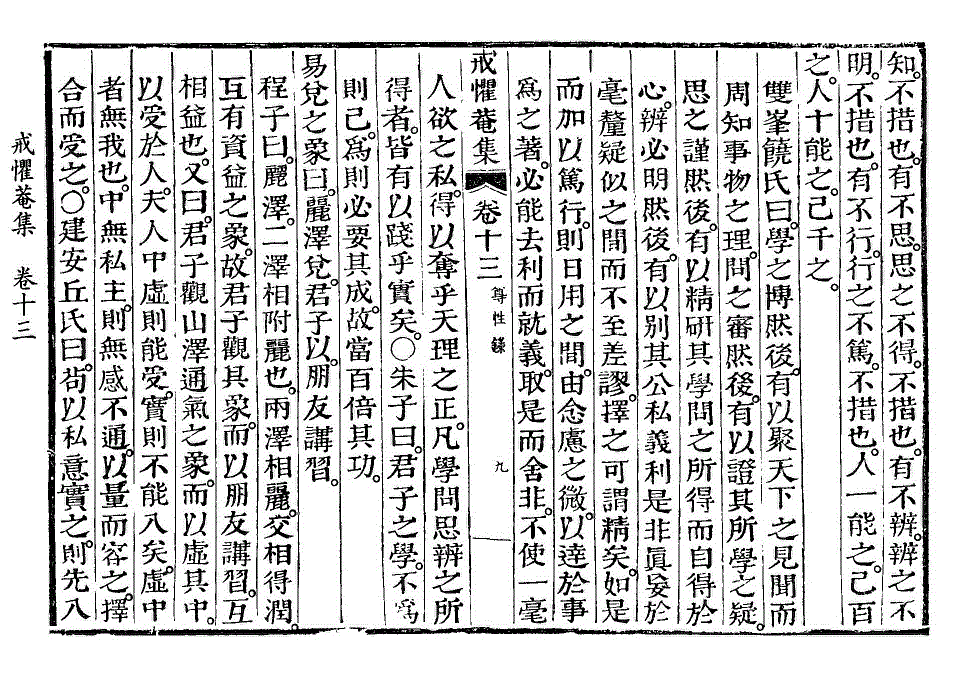 知。不措也。有不思。思之不得。不措也。有不辨。辨之不明。不措也。有不行。行之不笃。不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知。不措也。有不思。思之不得。不措也。有不辨。辨之不明。不措也。有不行。行之不笃。不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双峰饶氏曰。学之博然后。有以聚天下之见闻而周知事物之理。问之审然后。有以證其所学之疑。思之谨然后。有以精研其学问之所得而自得于心。辨必明然后。有以别其公私义利是非真妄于毫釐疑似之间而不至差谬。择之可谓精矣。如是而加以笃行。则日用之间。由念虑之微。以达于事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义。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夺乎天理之正。凡学问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践乎实矣。○朱子曰。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当百倍其功。
易兑之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程子曰。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得润。互有资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又曰。君子观山泽通气之象。而以虚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虚则能受。实则不能入矣。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择合而受之。○建安丘氏曰。苟以私意实之。则先入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09L 页
 者为主。而感应之机窒。虽有至者。皆捍而不受。
者为主。而感应之机窒。虽有至者。皆捍而不受。张子曰。义理有疑。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有所开。则即须劄记。不思则还塞矣。更须得朋友之助。一日间意思差别。须日日如此讲论大。则自觉进也。
朱子曰。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验得。非虚语也。
又曰。小学书纲领甚好。最切于日用。虽至大学之成。亦不外是。又曰。先读大学。以定其规谟。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首尾通贯。都无所疑然后。可读语孟。又无所疑然后。可读中庸。
张子曰。六经须循环熟读。理曾义理终无穷。
(已上论学问思辨之要。右穷理章)
按穷理力行。譬如轮翼之不可废一。其工夫要当一时并进。既论穷理之后。又当并加力行之功。故此章备言格致之方。而下章详论践履之实焉。
[力行章]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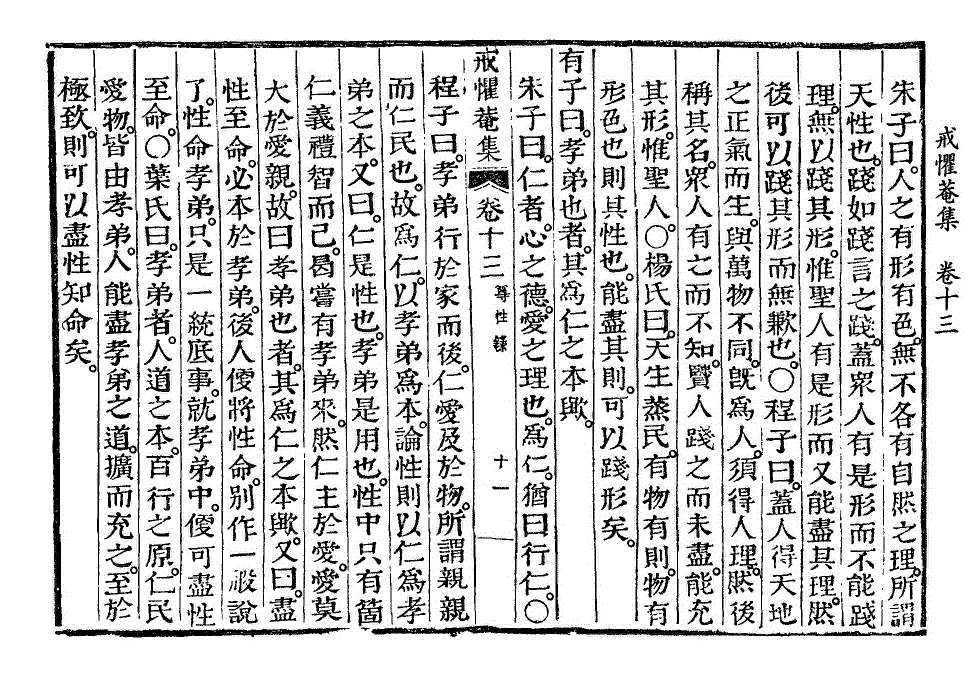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盖众人有是形而不能践理。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程子曰。盖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得人理。然后称其名。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充其形。惟圣人。○杨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物有形色也则其性也。能尽其则。可以践形矣。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盖众人有是形而不能践理。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程子曰。盖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得人理。然后称其名。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充其形。惟圣人。○杨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物有形色也则其性也。能尽其则。可以践形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为仁。犹曰行仁。○程子曰。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又曰。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又曰。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叶氏曰。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爱物。皆由孝弟。人能尽孝弟之道。扩而充之。至于极致。则可以尽性知命矣。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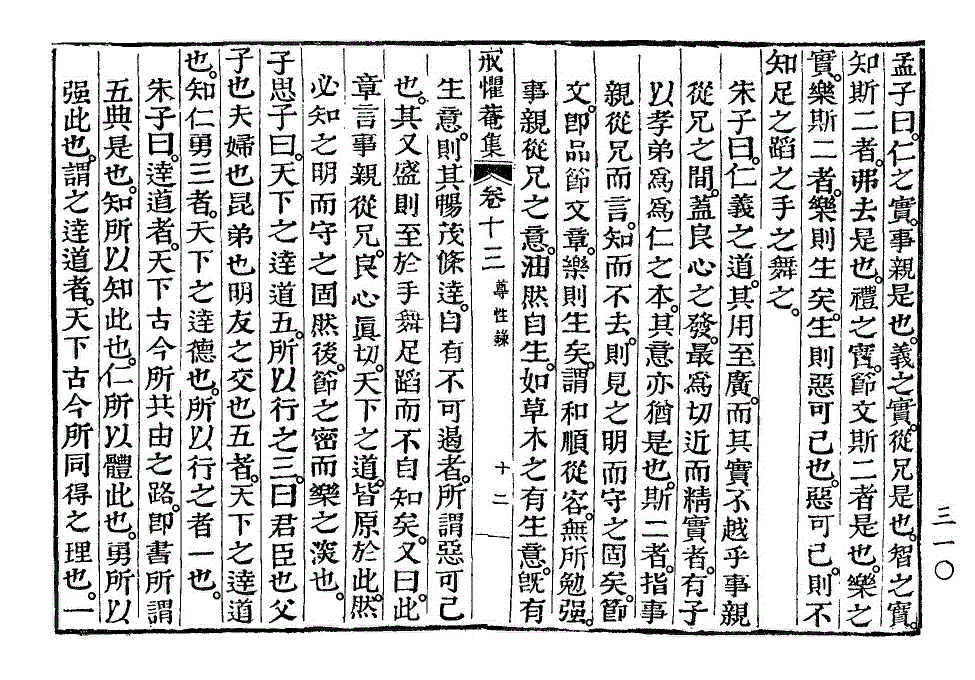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朱子曰。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其意亦犹是也。斯二者。指事亲从兄而言。知而不去。则见之明而守之固矣。节文。即品节文章。乐则生矣。谓和顺从容。无所勉强。事亲从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则其畅茂条达。自有不可遏者。所谓恶可已也。其又盛则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又曰。此章言事亲从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后。节之密而乐之深也。
子思子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1H 页
 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成。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谓诚。只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蔡氏曰。达道本于达德。达德本于诚。诚者达道达德之本。而一贯乎达道达德者也。
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成。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谓诚。只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蔡氏曰。达道本于达德。达德本于诚。诚者达道达德之本。而一贯乎达道达德者也。(已上言力行。以尽人伦为重。)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曰。拳拳。奉持之貌。服犹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朱子曰。终食者。一饭之顷。造次。急遽苟且之时。颠沛。倾覆流离之际。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无时无处而不仁也。○叶氏曰。不求速成。不容半涂而废。勉焉孳孳。死而后已可也。
张子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叶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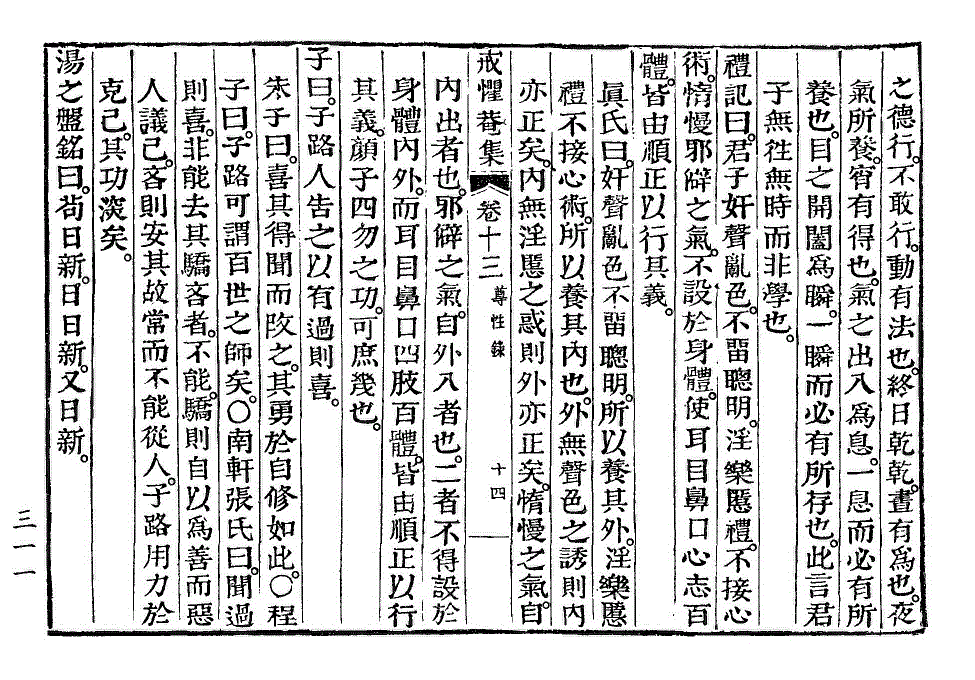 之德行。不敢行。动有法也。终日乾乾。昼有为也。夜气所养。宵有得也。气之出入为息。一息而必有所养也。目之开阖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无往无时而非学也。
之德行。不敢行。动有法也。终日乾乾。昼有为也。夜气所养。宵有得也。气之出入为息。一息而必有所养也。目之开阖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无往无时而非学也。礼记曰。君子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志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真氏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所以养其外。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所以养其内也。外无声色之诱则内亦正矣。内无淫慝之惑则外亦正矣。惰慢之气。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气。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设于身体内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颜子四勿之功。可庶几也。
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朱子曰。喜其得闻而改之。其勇于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可谓百世之师矣。○南轩张氏曰。闻过则喜。非能去其骄吝者。不能。骄则自以为善而恶人议己。吝则安其故常而不能从人。子路用力于克己。其功深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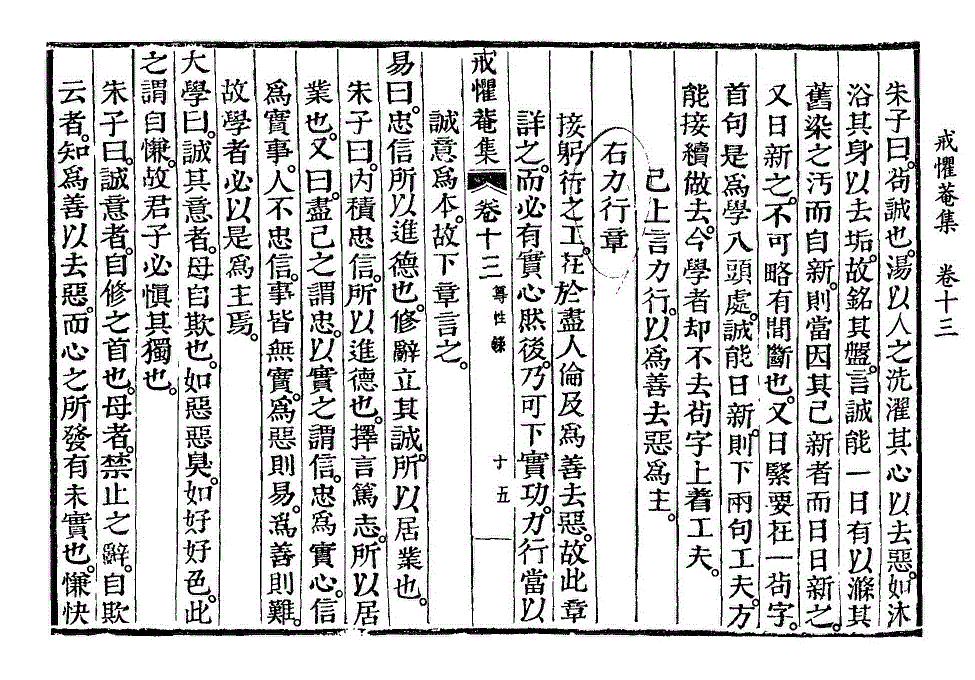 朱子曰。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又日紧要在一苟字。首句是为学入头处。诚能日新。则下两句工夫。方能接续做去。今学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工夫。
朱子曰。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又日紧要在一苟字。首句是为学入头处。诚能日新。则下两句工夫。方能接续做去。今学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工夫。(已上言力行。以为善去恶为主。右力行章)
接躬行之工。在于尽人伦及为善去恶。故此章详之。而必有实心然后。乃可下实功。力行当以诚意为本。故下章言之。
[诚意章]
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朱子曰。内积忠信。所以进德也。择言笃志。所以居业也。又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为实心。信为实事。人不忠信。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
大学曰。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朱子曰。诚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慊快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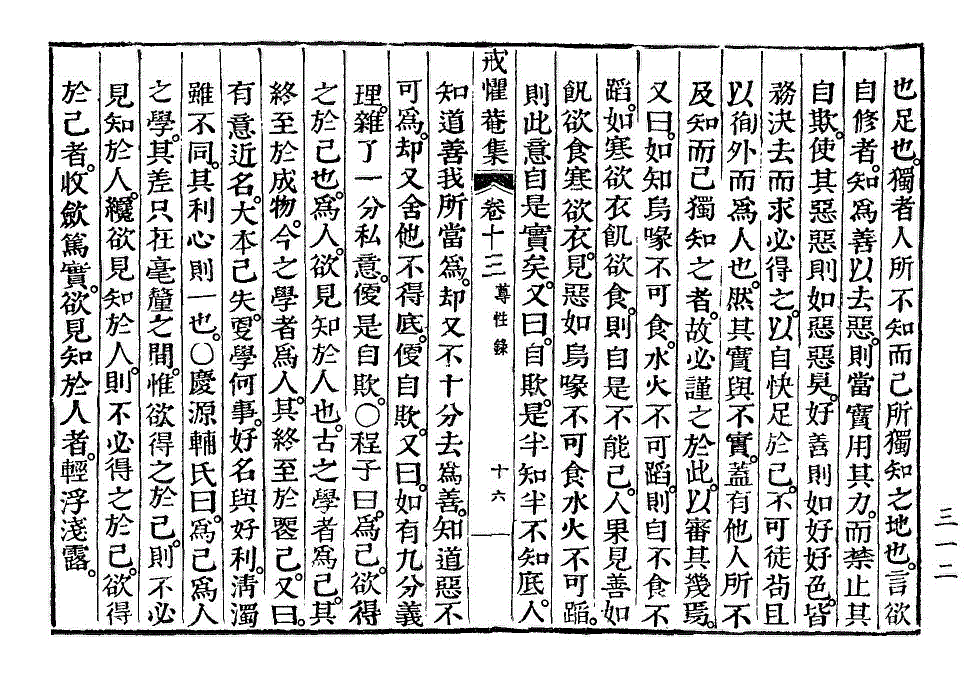 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又曰。如知乌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则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饥欲食。则自是不能已。人果见善如饥欲食寒欲衣。见恶如乌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则此意自是实矣。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当为。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为。却又舍他不得底。便自欺。又曰。如有九分义理。杂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又曰。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好名与好利。清浊虽不同。其利心则一也。○庆源辅氏曰。为己为人之学。其差只在毫釐之间。惟欲得之于己。则不必见知于人。才欲见知于人。则不必得之于己。欲得于己者。收敛笃实。欲见知于人者。轻浮浅露。
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又曰。如知乌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则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饥欲食。则自是不能已。人果见善如饥欲食寒欲衣。见恶如乌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则此意自是实矣。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当为。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为。却又舍他不得底。便自欺。又曰。如有九分义理。杂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又曰。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好名与好利。清浊虽不同。其利心则一也。○庆源辅氏曰。为己为人之学。其差只在毫釐之间。惟欲得之于己。则不必见知于人。才欲见知于人。则不必得之于己。欲得于己者。收敛笃实。欲见知于人者。轻浮浅露。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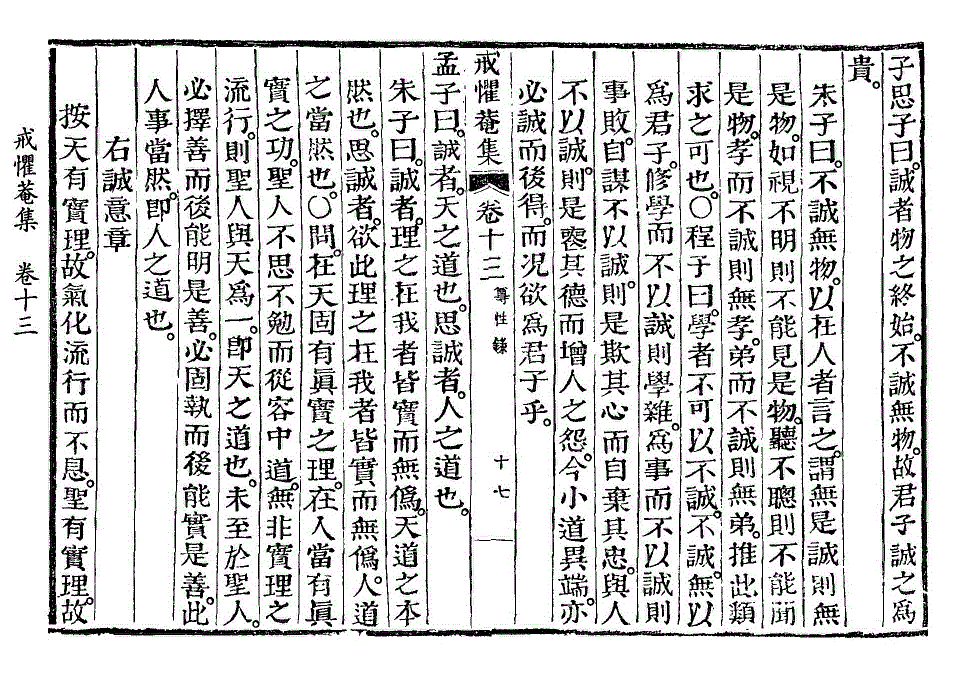 子思子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
子思子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朱子曰。不诚无物。以在人者言之。谓无是诚则无是物。如视不明则不能见是物。听不聪则不能闻是物。孝而不诚则无孝。弟而不诚则无弟。推此类求之可也。○程子曰。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而不以诚则学杂。为事而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乎。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朱子曰。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问。在天固有真实之理。在人当有真实之功。圣人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无非实理之流行。则圣人与天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于圣人。必择善而后能明是善。必固执而后能实是善。此人事当然。即人之道也。
(右诚意章)
按天有实理。故气化流行而不息。圣有实理。故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3L 页
 工夫缉熙而无间。学者若无实心。则其何能笃行而尽性乎。有亲有兄者。莫不知当孝当弟。而能孝弟者寡。有妻有子者。莫不知当敬当信。而能敬信者鲜。至于见善当好而如好好色者蔑如。见恶当去而如恶恶臭者谁也。又或强仁强义。外似可观。而中心所乐。不在仁义。矫伪难久。始锐终怠。如此之类。皆无实心故也。一心不实。万事皆假。何往而可行。一心苟实。万事皆诚。何为而不成。今玆别为一条于力行之下。而诚之意。实贯上下诸条。如理非诚则难格。气质非诚则难变。敬非诚则难熟。他可推见也。虽然。既诚于为学。而又须矫治气质之偏然后。可复本然之性而极其力行之功。故以矫气质次于下章。
工夫缉熙而无间。学者若无实心。则其何能笃行而尽性乎。有亲有兄者。莫不知当孝当弟。而能孝弟者寡。有妻有子者。莫不知当敬当信。而能敬信者鲜。至于见善当好而如好好色者蔑如。见恶当去而如恶恶臭者谁也。又或强仁强义。外似可观。而中心所乐。不在仁义。矫伪难久。始锐终怠。如此之类。皆无实心故也。一心不实。万事皆假。何往而可行。一心苟实。万事皆诚。何为而不成。今玆别为一条于力行之下。而诚之意。实贯上下诸条。如理非诚则难格。气质非诚则难变。敬非诚则难熟。他可推见也。虽然。既诚于为学。而又须矫治气质之偏然后。可复本然之性而极其力行之功。故以矫气质次于下章。[矫气质章]
洪范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沉潜刚克。高明柔克。
蔡氏曰。沉潜者。沉深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过乎中者也。平康正直。无所事乎矫拂也。沉潜刚克。以刚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刚也。○朱子曰。克治也。资质沉潜者。当以刚治之。资质高明者。当以柔治之。○黄氏曰。为学。须随其气质。察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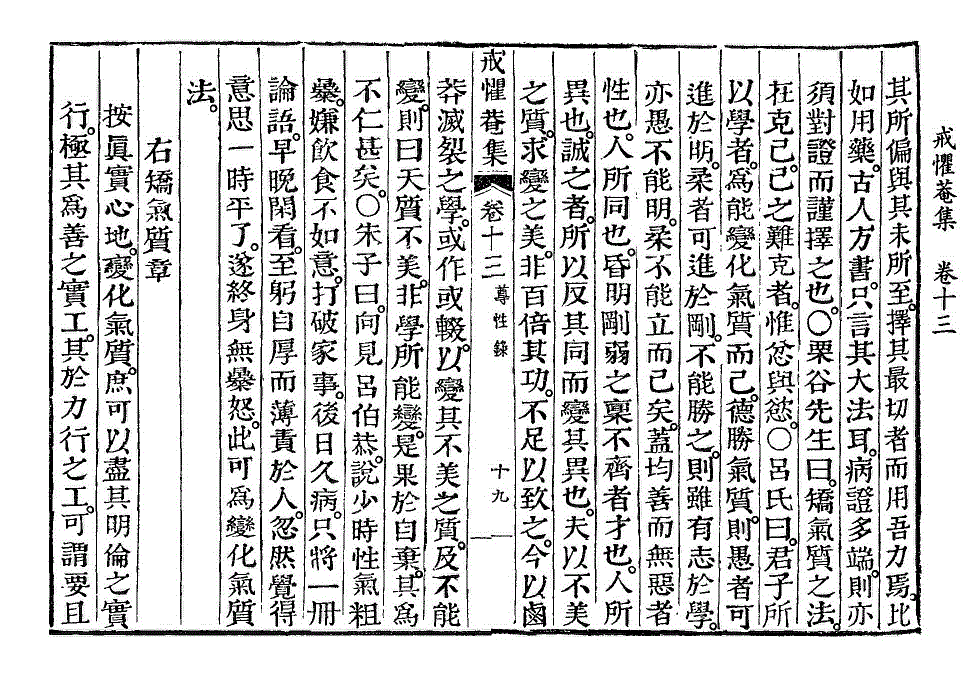 其所偏与其未所至。择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比如用药。古人方书。只言其大法耳。病證多端。则亦须对證而谨择之也。○栗谷先生曰。矫气质之法。在克己。己之难克者。惟忿与欲。○吕氏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刚。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刚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之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朱子曰。向见吕伯恭。说少时性气粗㬥。嫌饮食不如意。打破家事。后日久病。只将一册论语。早晚闲看。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然觉得意思一时平了。遂终身无㬥怒。此可为变化气质法。
其所偏与其未所至。择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比如用药。古人方书。只言其大法耳。病證多端。则亦须对證而谨择之也。○栗谷先生曰。矫气质之法。在克己。己之难克者。惟忿与欲。○吕氏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刚。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刚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之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朱子曰。向见吕伯恭。说少时性气粗㬥。嫌饮食不如意。打破家事。后日久病。只将一册论语。早晚闲看。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然觉得意思一时平了。遂终身无㬥怒。此可为变化气质法。(右矫气质章)
按真实心地。变化气质。庶可以尽其明伦之实行。极其为善之实工。其于力行之工。可谓要且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4L 页
 切矣。故此章言之备矣。大抵力行。固以明伦践善为用力之地。而又当以存养克复为微密工夫。故复以已发处遏欲未发时存性。为力行上微密之工而次于下章。
切矣。故此章言之备矣。大抵力行。固以明伦践善为用力之地。而又当以存养克复为微密工夫。故复以已发处遏欲未发时存性。为力行上微密之工而次于下章。[正心章]
周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蔡氏曰。圣固未易为也。狂而克念。则作圣之功。知所向方。圣固无所谓罔念。一念之差。虽未至于狂。而作狂之理。亦在是矣。
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惟心之谓欤。
朱子曰。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危动难安如此。又曰。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亡所致也。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
子思子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子曰。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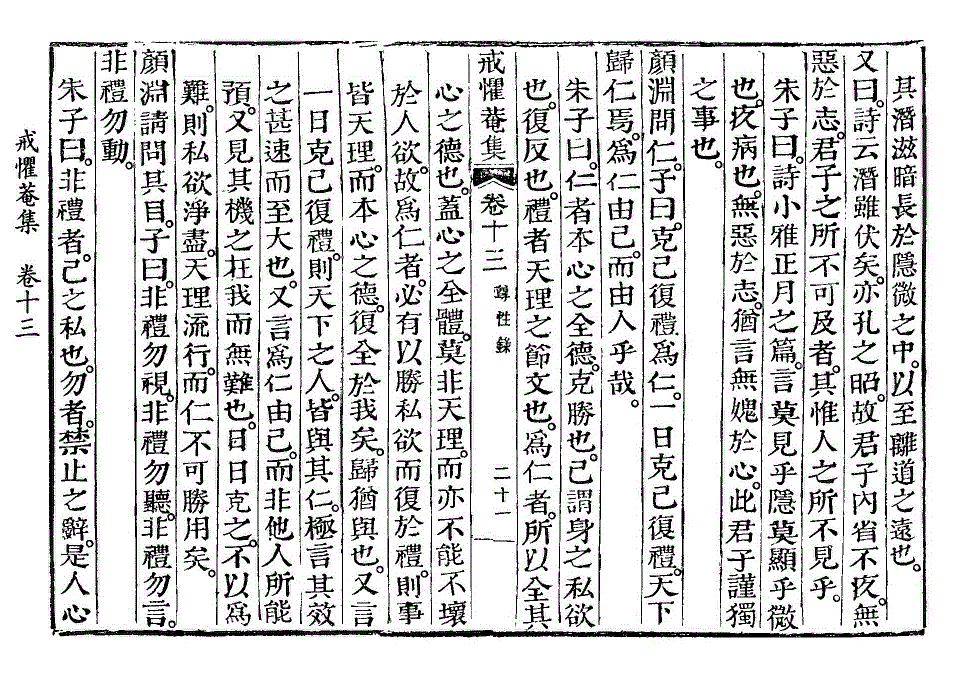 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又曰。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朱子曰。诗小雅正月之篇。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疚病也。无恶于志。犹言无愧于心。此君子谨独之事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体。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
颜渊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朱子曰。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5L 页
 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曰。非礼而勿视听者。防其自外入而动于内者也。非礼而勿言动者。谨其自内出而接于外者也。内外交进。为仁之功。不遗馀力矣。其机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克念则为圣。自是而罔念则为狂。特毫忽之间耳。学者可不谨其所操哉。又曰。非礼之色。虽过乎前。不可有视之之心。非礼之声。虽过乎耳。不可有听之之心。○程子曰。视听言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已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
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曰。非礼而勿视听者。防其自外入而动于内者也。非礼而勿言动者。谨其自内出而接于外者也。内外交进。为仁之功。不遗馀力矣。其机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克念则为圣。自是而罔念则为狂。特毫忽之间耳。学者可不谨其所操哉。又曰。非礼之色。虽过乎前。不可有视之之心。非礼之声。虽过乎耳。不可有听之之心。○程子曰。视听言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已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6H 页
 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人同归。○朱子奏劄曰。臣愿陛下一念之萌。则必谨之察之。此为天理耶。此为人欲耶。果天理耶。则敬而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耶。则敬而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其为是。则行之惟恐其不力。知其为非。则去之惟恐其不果。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程子曰。甚哉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声。以至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逸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惟思而能窒欲。曾子三省之道也。
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人同归。○朱子奏劄曰。臣愿陛下一念之萌。则必谨之察之。此为天理耶。此为人欲耶。果天理耶。则敬而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耶。则敬而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其为是。则行之惟恐其不力。知其为非。则去之惟恐其不果。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程子曰。甚哉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声。以至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逸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惟思而能窒欲。曾子三省之道也。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者。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使是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6L 页
 欲。又曰。人于天理昏者。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说却最是。又曰。凡百玩好皆夺志。书札于儒者为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日精力一用于此。非唯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足知丧志也。○栗谷曰。寡欲之欲。泛指心所欲言。虽曰人之所不能无者。但多而不节。便是私欲。
欲。又曰。人于天理昏者。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说却最是。又曰。凡百玩好皆夺志。书札于儒者为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日精力一用于此。非唯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足知丧志也。○栗谷曰。寡欲之欲。泛指心所欲言。虽曰人之所不能无者。但多而不节。便是私欲。(已上言已发时遏人欲。)
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朱子曰。不睹不闻。便是喜怒哀乐未发处。常要提起此心在这里。防于未然。又曰。戒惧不须说太重。只是收拾来。便在这里。伊川所谓敬字也。○西山真氏曰。戒谨恐惧。只是事物未形之间。常常持敬。令不昏昧而已。思虑未形。而知觉不昧。性之体段。自有不可掩者。程子所谓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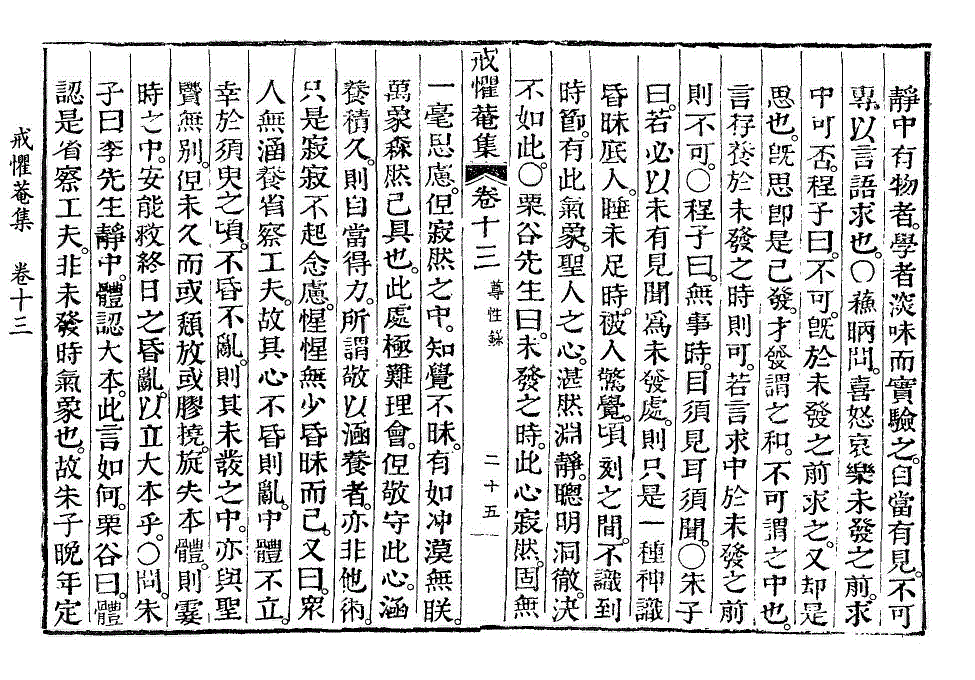 静中有物者。学者深味而实验之。自当有见。不可专以言语求也。○苏炳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于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言存养于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程子曰。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到时节。有此气象。圣人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栗谷先生曰。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眹。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又曰。众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挠。旋失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问。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言如何。栗谷曰。体认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
静中有物者。学者深味而实验之。自当有见。不可专以言语求也。○苏炳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于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言存养于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程子曰。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到时节。有此气象。圣人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栗谷先生曰。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眹。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又曰。众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挠。旋失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问。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言如何。栗谷曰。体认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7L 页
 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
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又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朱子曰。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敬信。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北溪陈氏曰。抑诗。即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之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处盖己之所不睹。须是真实无妄。常如戒惧。方能无愧怍。君子为己之功至此。不待动而应接。方是敬也。盖于未应接之前。已无非敬矣。不待发言而信实。盖于未发言之前。本来真实。无非信实矣。
(已上言未发时天理。右正心章)
按此章。论遏欲存理。以正其心者。为行之微密工夫也。或有疑存天理遏人欲。不可谓之行者。然孟子以存心养性。对尽心知性而谓之践履。大学以正心诚意。对格物致知而谓之行。存性遏欲。其非存养诚正之功耶。以此言之。存天理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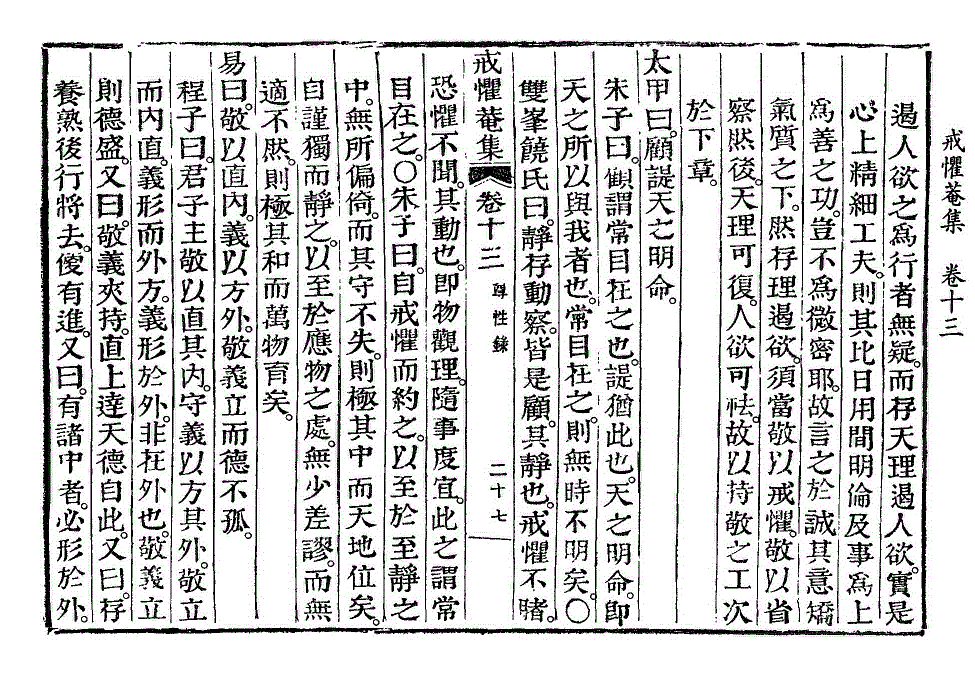 遏人欲之为行者无疑。而存天理遏人欲。实是心上精细工夫。则其比日用间明伦及事为上为善之功。岂不为微密耶。故言之于诚其意矫气质之下。然存理遏欲。须当敬以戒惧。敬以省察然后。天理可复。人欲可祛。故以持敬之工次于下章。
遏人欲之为行者无疑。而存天理遏人欲。实是心上精细工夫。则其比日用间明伦及事为上为善之功。岂不为微密耶。故言之于诚其意矫气质之下。然存理遏欲。须当敬以戒惧。敬以省察然后。天理可复。人欲可祛。故以持敬之工次于下章。[持敬章]
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朱子曰。顾谓常目在之也。諟犹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双峰饶氏曰。静存动察。皆是顾。其静也。戒惧不睹。恐惧不闻。其动也。即物观理。随事度宜。此之谓常目在之。○朱子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静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
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立则德盛。又曰。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又曰。存养熟后行将去。便有进。又曰。有诸中者。必形于外。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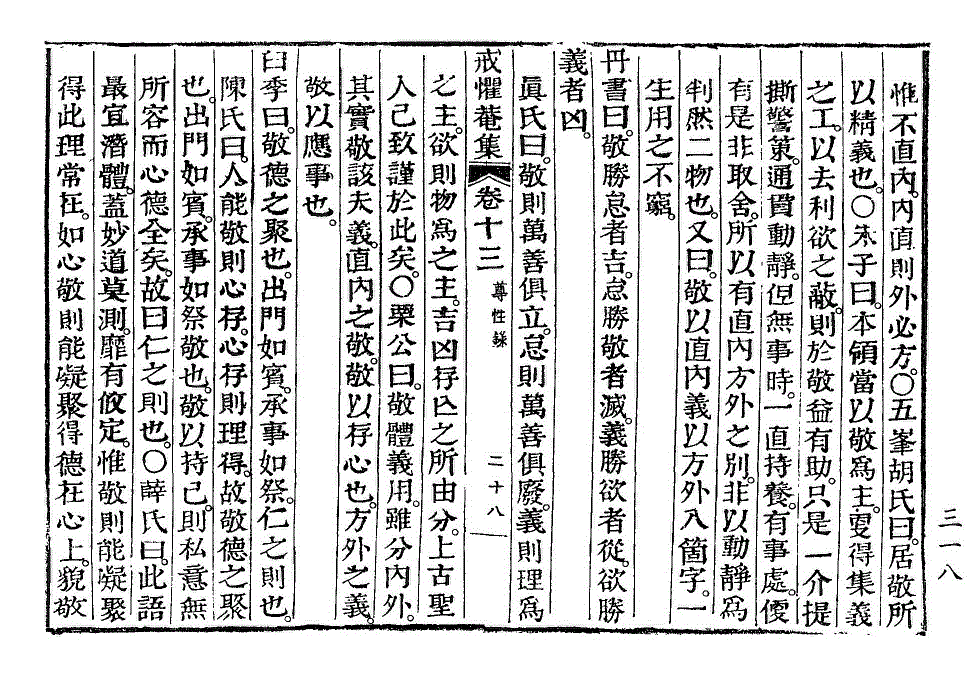 惟不直内。内直则外必方。○五峰胡氏曰。居敬所以精义也。○朱子曰。本领当以敬为主。更得集义之工。以去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只是一介提撕警策。通贯动静。但无事时。一直持养。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别。非以动静为判然二物也。又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入个字。一生用之不穷。
惟不直内。内直则外必方。○五峰胡氏曰。居敬所以精义也。○朱子曰。本领当以敬为主。更得集义之工。以去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只是一介提撕警策。通贯动静。但无事时。一直持养。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别。非以动静为判然二物也。又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入个字。一生用之不穷。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真氏曰。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义则理为之主。欲则物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圣人已致谨于此矣。○栗公曰。敬体义用。虽分内外。其实敬该夫义。直内之敬。敬以存心也。方外之义。敬以应事也。
臼季曰。敬德之聚也。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陈氏曰。人能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得。故敬德之聚也。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敬也。敬以持己。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故曰仁之则也。○薛氏曰。此语最宜潜体。盖妙道莫测。靡有攸定。惟敬则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则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9H 页
 则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类。莫不皆然。或有不敬。则心君放逸。而百体解弛。虽曰有人之形。而其实块然血气之体。与物无以异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为践形尽性之要也。
则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类。莫不皆然。或有不敬。则心君放逸。而百体解弛。虽曰有人之形。而其实块然血气之体。与物无以异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为践形尽性之要也。程子曰。敬胜百邪。
朱子曰。敬是扶策人底道理。人当怠惰放肆时。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虽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听。又曰。敬所以抵敌人欲。人常敬则天理自明。人欲上来不得。○三山陈氏曰。隐伏之间。理甚昭明。君子内省此处。须无一毫疚病。方无愧于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于独致其谨耳。
(已上言敬之能存性遏欲。)
按敬固为存性遏欲之本。故于此先为条论。而敬之工夫及敬之察病加工。又自有其方。故于下历言之。盖上所言收放心之敬。是敬初头之工。此所言戒惧慎独。是敬成就之工。敬之一字。乃为圣学之成始成终者。可见矣。
程子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
问。主一无适。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头万绪。学问只要专一。○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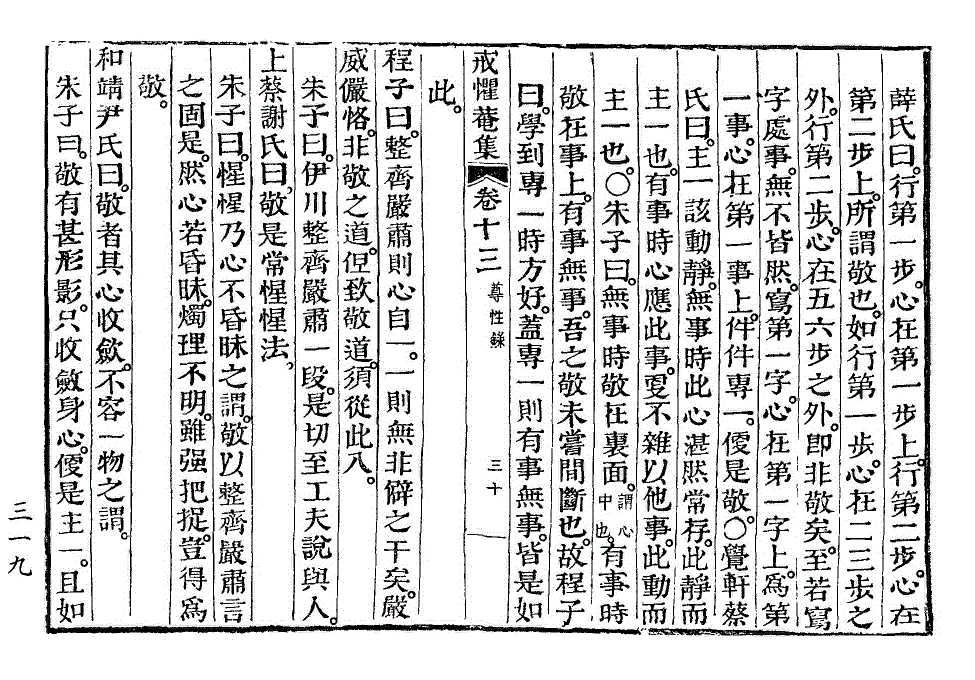 薛氏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所谓敬也。如行第一步。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心在五六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写字处事。无不皆然。写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为第一事。心在第一事上。件件专一。便是敬。○觉轩蔡氏曰。主一该动静。无事时此心湛然常存。此静而主一也。有事时心应此事。更不杂以他事。此动而主一也。○朱子曰。无事时敬在里面。(谓心中也。)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故程子曰。学到专一时方好。盖专一则有事无事。皆是如此。
薛氏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所谓敬也。如行第一步。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心在五六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写字处事。无不皆然。写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为第一事。心在第一事上。件件专一。便是敬。○觉轩蔡氏曰。主一该动静。无事时此心湛然常存。此静而主一也。有事时心应此事。更不杂以他事。此动而主一也。○朱子曰。无事时敬在里面。(谓心中也。)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故程子曰。学到专一时方好。盖专一则有事无事。皆是如此。程子曰。整齐严肃则心自一。一则无非僻之干矣。严威俨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道。须从此入。
朱子曰。伊川整齐严肃一段。是切至工夫说与人。
上蔡谢氏曰。敬是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敬以整齐严肃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
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之谓。
朱子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0H 页
 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着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或问。三先生言敬之异。朱子曰。比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从一方入至此。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矣。
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着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或问。三先生言敬之异。朱子曰。比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从一方入至此。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矣。朱子曰。敬是常悚然如有所畏之意。常若有畏。则不敢自欺而近于敬矣。
勉斋黄氏曰。敬者主一无适之谓。程子语也。然师说又以敬字惟畏为近之。盖敬者。心主于一。如入宗庙见君父之时。自无杂念。闲居放肆之际。念虑纷挠而不主于一矣。二说盖相表里。学者体之则可见矣。○张子曰。正心之始。当以己心为严师。凡有动作。则知所惧。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则自然心正。○觉轩蔡氏曰。人之一心。虚灵知觉。常肃然而不乱。炯然而不昏。则寂而理之体无不存。感而理之用无不行。惟夫虚灵知觉。不能不动于欲。则此心之体用。将随之而昏且乱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师之临其上。深渊薄冰之处其下。则虚灵知觉。自不容于昏且乱矣。此敬字之义。所以惟畏为近之。
朱子敬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0L 页
 上帝。(此言静无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言能折旋于挟小之地也。此言动无违。)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此言表之正。)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此言里之正。)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此言心之主一而达于事。)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诚惟一。万变是监。(此言事之主一而本于心。)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此揔结上文。)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熟。不冰而寒。(须臾以时言。此言心不能无适之病。)毫釐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毫釐以事言。此言事不能主一之病。)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乡司戒。敢告灵台。
上帝。(此言静无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言能折旋于挟小之地也。此言动无违。)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此言表之正。)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此言里之正。)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此言心之主一而达于事。)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诚惟一。万变是监。(此言事之主一而本于心。)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此揔结上文。)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熟。不冰而寒。(须臾以时言。此言心不能无适之病。)毫釐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毫釐以事言。此言事不能主一之病。)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乡司戒。敢告灵台。西山真氏曰。敬之为义。至是无复馀蕴。有志于圣学者。宜熟玩之。
(已上言敬之工夫。)
朱子曰。整顿收敛。则入于着力。从容游泳。又堕于悠泛。此正学者之通患。然程子尝论之曰。亦须且自此去。到德盛后。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当且就整顿收敛处着力。但不可安排等候。即成病矣。
朱子曰。今人将敬来别做一事。所以有厌倦。且为思虑引去。敬只是自家一个心常惺惺。不可将来别做一事。○先生问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学静坐。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1H 页
 痛抑思虑。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放退只是不为念虑所牵而俱往也。)也不可全无思虑。无邪思耳。○问。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觉衰飒。不知当如何。曰。这个也不须。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个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来。便是敬。○又曰。心无不敬。则四体自然收敛。不得着意安排。而四体亦自舒适矣。着意安排。则难久而生病矣。
痛抑思虑。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放退只是不为念虑所牵而俱往也。)也不可全无思虑。无邪思耳。○问。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觉衰飒。不知当如何。曰。这个也不须。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个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来。便是敬。○又曰。心无不敬。则四体自然收敛。不得着意安排。而四体亦自舒适矣。着意安排。则难久而生病矣。朱子曰。静中私意横生。此学者之通患。当以敬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为何事。就其重处。痛加惩窒。久之纯熟。自当见效。
朱子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晓。又从旁别生一小念。渐渐放阔去。不可不察。○问。静坐久之。一念不免发动。如何。曰。也须看一念要做甚么事。若是好事。当做须去干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自觉得如此。这敬便在这里。○栗谷曰。学者之用工。最难得效者。在于浮念。盖恶念虽实。苟能诚于为善。则治之亦易。惟浮念则无事之时。倏起倏灭。有不得自由者。夫以温公之诚意。尚患纷乱。况初学乎。学者须常主于敬。顷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于当止。无事静坐时。若有念头之发。则必即省觉。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1L 页
 若是恶念。勇猛断绝。不留苗脉。若是善念而事当思惟者。则穷究其理。了其未了者。使此理预明。若不管利害之念。或虽善念而非其时者。则此是浮念也。浮念之发。有意厌恶。则尤见扰乱。且此厌恶之心。亦是浮念。觉得是浮念后。只可轻轻放退。提掇此心。勿与俱往。则才发复息矣。如是用工。日夕乾乾。不求速成。不生懈怠。如未得力。或有闷郁无聊之时。亦须抖擞精神。洗濯心地。使无一念。以来清和气象。久久纯熟。至于凝定。则常觉此心卓然有立。不为事物所牵累。而本体之明。无所掩蔽。睿智所照。权度不差矣。最不可遽期朝夕之效。而不效则辄生退隳之心也。
若是恶念。勇猛断绝。不留苗脉。若是善念而事当思惟者。则穷究其理。了其未了者。使此理预明。若不管利害之念。或虽善念而非其时者。则此是浮念也。浮念之发。有意厌恶。则尤见扰乱。且此厌恶之心。亦是浮念。觉得是浮念后。只可轻轻放退。提掇此心。勿与俱往。则才发复息矣。如是用工。日夕乾乾。不求速成。不生懈怠。如未得力。或有闷郁无聊之时。亦须抖擞精神。洗濯心地。使无一念。以来清和气象。久久纯熟。至于凝定。则常觉此心卓然有立。不为事物所牵累。而本体之明。无所掩蔽。睿智所照。权度不差矣。最不可遽期朝夕之效。而不效则辄生退隳之心也。(已上论敬之察病加工。右持敬章)
按以敬为主。尽袪私邪。则天理可复。心体乃全。而驯致不思不勉从容中道之域矣。然又当申言诚者天道之事。以极其务实之效笃恭之妙。以明复性之极功。故此章既论持敬之方。而下章以至诚终焉。
[至诚章]
子思子曰。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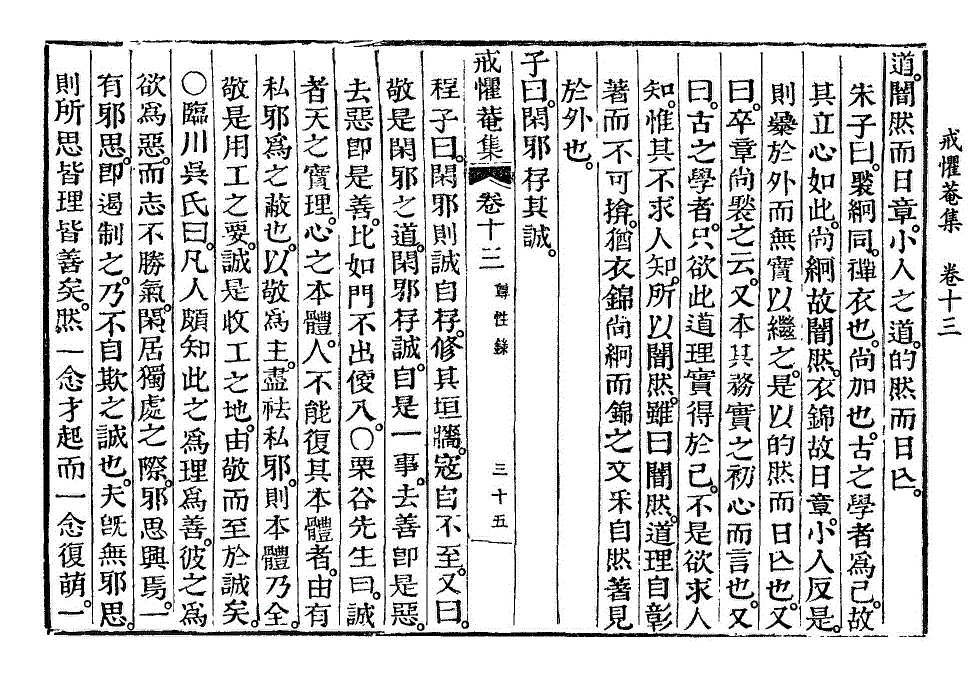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朱子曰。褧絅同。禅衣也。尚加也。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锦故日章。小人反是。则㬥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又曰。卒章尚褧之云。又本其务实之初心而言也。又曰。古之学者。只欲此道理实得于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虽曰闇然。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犹衣锦尚絅而锦之文采自然著见于外也。
子曰。闲邪存其诚。
程子曰。闲邪则诚自存。修其垣墙。寇自不至。又曰。敬是闲邪之道。闲邪存诚。自是一事。去善即是恶。去恶即是善。比如门不出便入。○栗谷先生曰。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人不能复其本体者。由有私邪为之蔽也。以敬为主。尽祛私邪。则本体乃全。敬是用工之要。诚是收工之地。由敬而至于诚矣。○临川吴氏曰。凡人颇知此之为理为善。彼之为欲为恶。而志不胜气。闲居独处之际。邪思兴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诚也。夫既无邪思。则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复萌。一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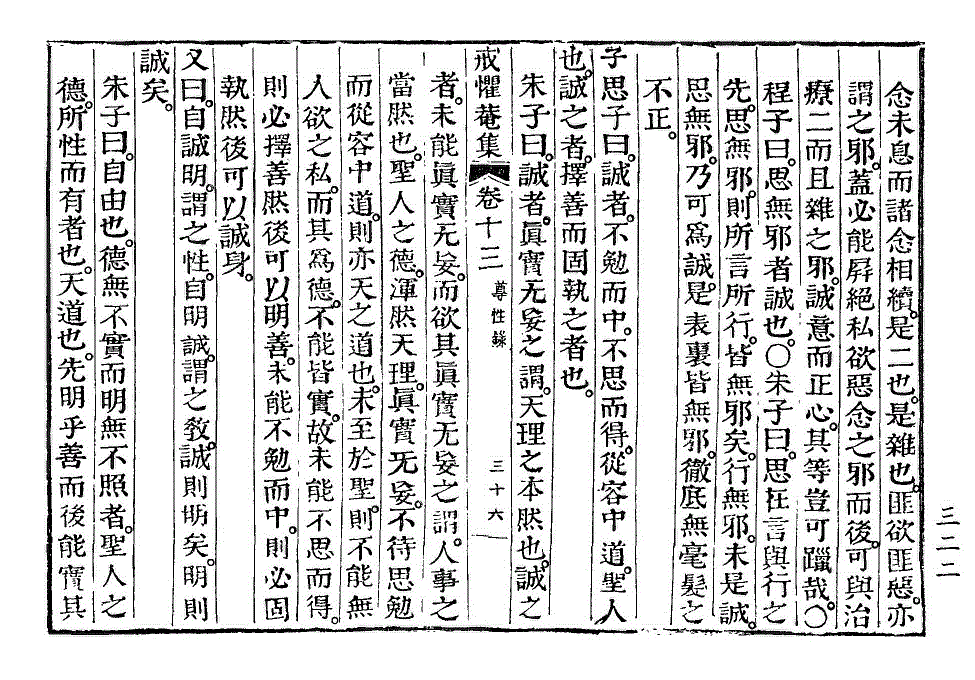 念未息而诸念相续。是二也。是杂也。匪欲匪恶。亦谓之邪。盖必能屏绝私欲恶念之邪而后。可与治疗二而且杂之邪。诚意而正心。其等岂可躐哉。○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朱子曰。思在言与行之先。思无邪。则所言所行。皆无邪矣。行无邪。未是诚。思无邪。乃可为诚。是表里皆无邪。彻底无毫发之不正。
念未息而诸念相续。是二也。是杂也。匪欲匪恶。亦谓之邪。盖必能屏绝私欲恶念之邪而后。可与治疗二而且杂之邪。诚意而正心。其等岂可躐哉。○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朱子曰。思在言与行之先。思无邪。则所言所行。皆无邪矣。行无邪。未是诚。思无邪。乃可为诚。是表里皆无邪。彻底无毫发之不正。子思子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朱子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
又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朱子曰。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3H 页
 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
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周子曰。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周子只说一者无欲也。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说个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挨去。庶几执捉得定。有下手处。又曰。一即所谓太极。静虚即阴静。动直即阳动。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又曰。一便是无欲。今试看无欲之时。心岂不一。或问。比程子主一之谓敬。如何。曰无欲与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颇似费力。○勉斋黄氏曰。一是纯一不杂之谓。○北溪陈氏曰。一者是表里俱一。纯彻无二。着纤毫私欲。便二矣。内一则静虚。外一则动直。而明通公溥则又无时不一也。一者此心浑然。太极之体。无欲者。心体粹然。无极之真。静虚者。体之未发。豁然无一物之累。阴之性也。动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阳之情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3L 页
 朱子曰。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又曰。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朱子曰。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又曰。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子思子曰。诗曰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朱子曰。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陈氏曰。笃恭。是申解不显二字。虽无人之境亦恭。是笃厚其敬也。○新安陈氏曰。不显笃恭。实原于尚絅闇然与慎独戒惧深密之功。
又曰。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朱子曰。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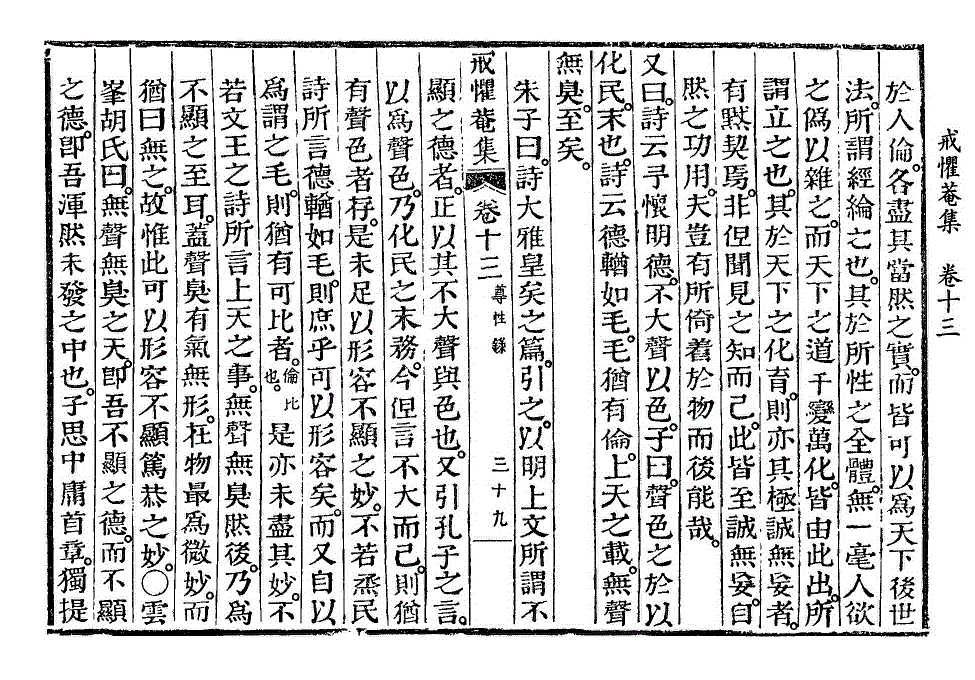 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下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
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下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又曰。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云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朱子曰。诗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今但言不大而已。则犹有声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不若烝民诗所言德輶如毛。则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为谓之毛。则犹有可比者。(伦比也。)是亦未尽其妙。不若文王之诗所言上天之事。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盖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显笃恭之妙。○云峰胡氏曰。无声无臭之天。即吾不显之德。而不显之德。即吾浑然未发之中也。子思中庸首章。独提
戒惧庵集卷之十三 第 3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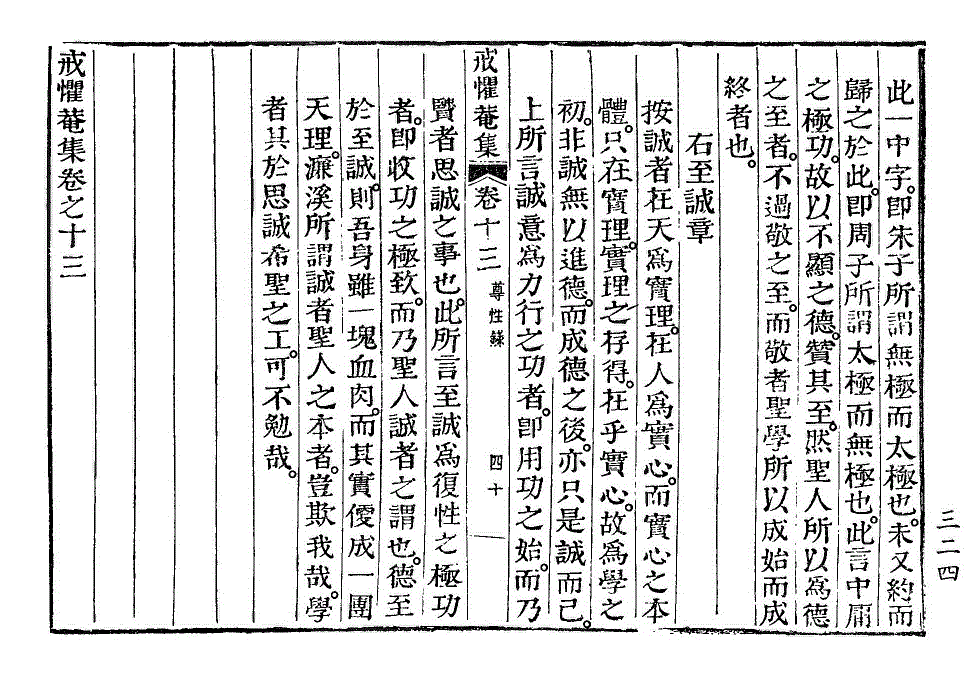 此一中字。即朱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未又约而归之于此。即周子所谓太极而无极也。此言中庸之极功。故以不显之德。赞其至。然圣人所以为德之至者。不过敬之至。而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此一中字。即朱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未又约而归之于此。即周子所谓太极而无极也。此言中庸之极功。故以不显之德。赞其至。然圣人所以为德之至者。不过敬之至。而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右至诚章)
按诚者在天为实理。在人为实心。而实心之本体。只在实理。实理之存得。在乎实心。故为学之初。非诚无以进德。而成德之后。亦只是诚而已。上所言诚意为力行之功者。即用功之始。而乃贤者思诚之事也。此所言至诚为复性之极功者。即收功之极致。而乃圣人诚者之谓也。德至于至诚。则吾身虽一块血肉。而其实便成一团天理。濂溪所谓诚者圣人之本者。岂欺我哉。学者其于思诚希圣之工。可不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