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x 页
戒惧庵集卷之二
书
书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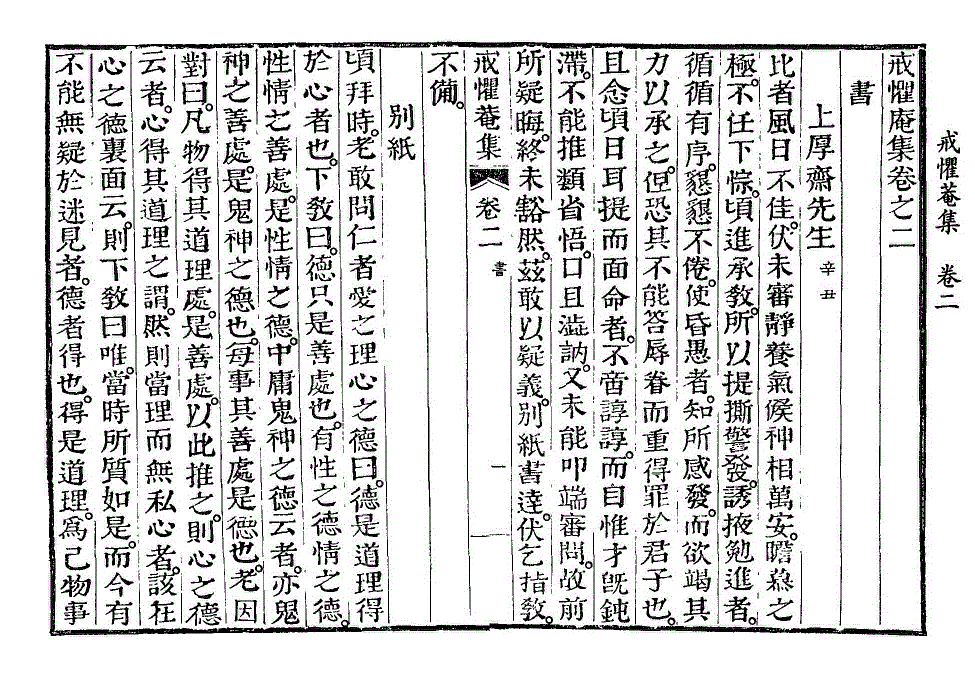 上厚斋先生(辛丑)
上厚斋先生(辛丑)比者风日不佳。伏未审静养气候神相万安。瞻慕之极。不任下悰。顷进承教。所以提撕警发。诱掖勉进者。循循有序。恳恳不倦。使昏愚者。知所感发。而欲竭其力以承之。但恐其不能答辱眷而重得罪于君子也。且念顷日耳提而面命者。不啻谆谆。而自惟才既钝滞。不能推类省悟。口且涩讷。又未能叩端审问。故前所疑晦。终未豁然。玆敢以疑义。别纸书达。伏乞指教。不备。
别纸
顷拜时。老敢问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曰。德是道理得于心者也。下教曰。德只是善处也。有性之德情之德。性情之善处。是性情之德。中庸鬼神之德云者。亦鬼神之善处。是鬼神之德也。每事其善处是德也。老因对曰。凡物得其道理处。是善处。以此推之。则心之德云者。心得其道理之谓。然则当理而无私心者。该在心之德里面云。则下教曰唯。当时所质如是。而今有不能无疑于迷见者。德者得也。得是道理。为己物事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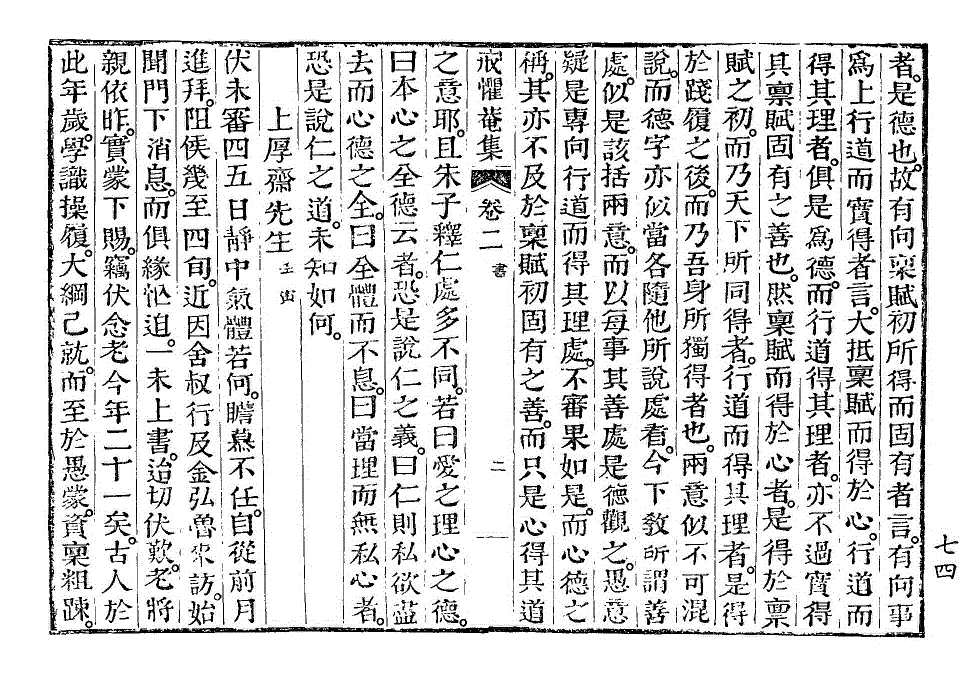 者。是德也。故有向禀赋初所得而固有者言。有向事为上行道而实得者言。大抵禀赋而得于心。行道而得其理者。俱是为德。而行道得其理者。亦不过实得其禀赋固有之善也。然禀赋而得于心者。是得于禀赋之初。而乃天下所同得者。行道而得其理者。是得于践履之后。而乃吾身所独得者也。两意似不可混说。而德字亦似当各随他所说处看。今下教所谓善处。似是该括两意。而以每事其善处是德观之。愚意疑是专向行道而得其理处。不审果如是。而心德之称。其亦不及于禀赋初固有之善。而只是心得其道之意耶。且朱子释仁处多不同。若曰爱之理心之德。曰本心之全德云者。恐是说仁之义。曰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曰全体而不息。曰当理而无私心者。恐是说仁之道。未知如何。
者。是德也。故有向禀赋初所得而固有者言。有向事为上行道而实得者言。大抵禀赋而得于心。行道而得其理者。俱是为德。而行道得其理者。亦不过实得其禀赋固有之善也。然禀赋而得于心者。是得于禀赋之初。而乃天下所同得者。行道而得其理者。是得于践履之后。而乃吾身所独得者也。两意似不可混说。而德字亦似当各随他所说处看。今下教所谓善处。似是该括两意。而以每事其善处是德观之。愚意疑是专向行道而得其理处。不审果如是。而心德之称。其亦不及于禀赋初固有之善。而只是心得其道之意耶。且朱子释仁处多不同。若曰爱之理心之德。曰本心之全德云者。恐是说仁之义。曰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曰全体而不息。曰当理而无私心者。恐是说仁之道。未知如何。上厚斋先生(壬寅)
伏未审四五日静中气体若何。瞻慕不任。自从前月进拜。阻候几至四旬。近因舍叔行及金弘鲁来访。始闻门下消息。而俱缘忙迫。一未上书。迨切伏叹。老将亲依昨。实蒙下赐。窃伏念老今年二十一矣。古人于此年岁。学识操履。大纲已就。而至于愚蒙。资禀粗疏。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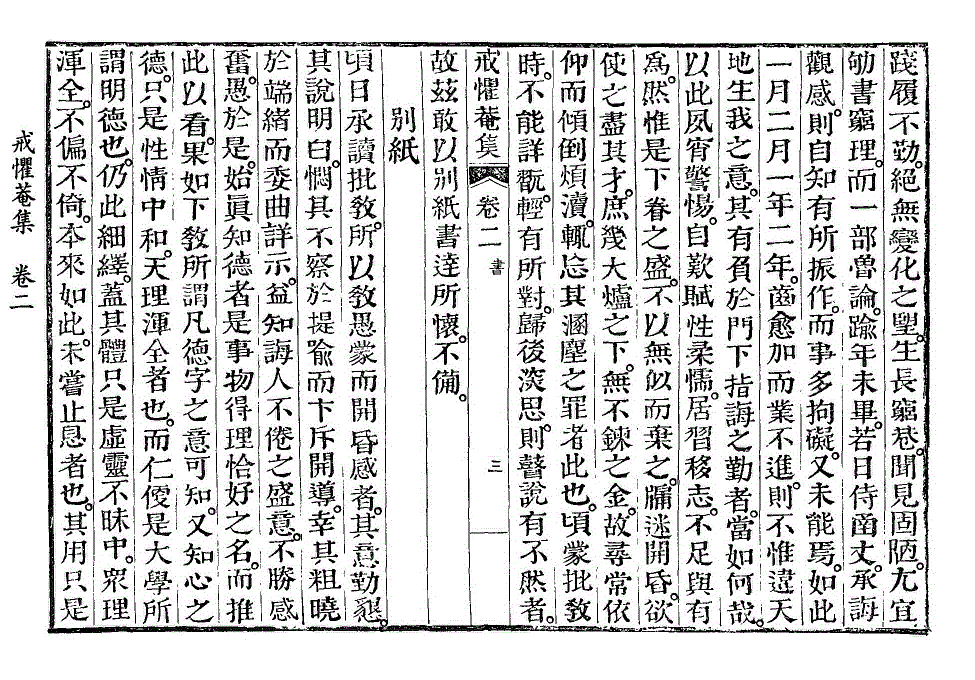 践履不勤。绝无变化之望。生长穷巷。闻见固陋。尤宜劬书穷理。而一部鲁论。踰年未毕。若日侍函丈。承诲观感。则自知有所振作。而事多拘碍。又未能焉。如此一月二月一年二年。齿愈加而业不进。则不惟违天地生我之意。其有负于门下指诲之勤者。当如何哉。以此夙宵警惕。自叹赋性柔懦。居习移志。不足与有为。然惟是下眷之盛。不以无似而弃之。牖迷开昏。欲使之尽其才。庶几大炉之下。无不鍊之金。故寻常依仰而倾倒烦渎。辄忘其溷尘之罪者此也。顷蒙批教时。不能详玩。轻有所对。归后深思。则瞽说有不然者。故兹敢以别纸书达所怀。不备。
践履不勤。绝无变化之望。生长穷巷。闻见固陋。尤宜劬书穷理。而一部鲁论。踰年未毕。若日侍函丈。承诲观感。则自知有所振作。而事多拘碍。又未能焉。如此一月二月一年二年。齿愈加而业不进。则不惟违天地生我之意。其有负于门下指诲之勤者。当如何哉。以此夙宵警惕。自叹赋性柔懦。居习移志。不足与有为。然惟是下眷之盛。不以无似而弃之。牖迷开昏。欲使之尽其才。庶几大炉之下。无不鍊之金。故寻常依仰而倾倒烦渎。辄忘其溷尘之罪者此也。顷蒙批教时。不能详玩。轻有所对。归后深思。则瞽说有不然者。故兹敢以别纸书达所怀。不备。别纸
顷日承读批教。所以教愚蒙而开昏感者。其意勤恳。其说明白。悯其不察于提喻而卞斥开导。幸其粗晓于端绪而委曲详示。益知诲人不倦之盛意。不胜感奋。愚于是。始真知德者是事物得理恰好之名。而推此以看。果如下教所谓凡德字之意可知。又知心之德。只是性情中和。天理浑全者也。而仁便是大学所谓明德也。仍此细绎。盖其体只是虚灵不昧中。众理浑全。不偏不倚。本来如此。未尝止息者也。其用只是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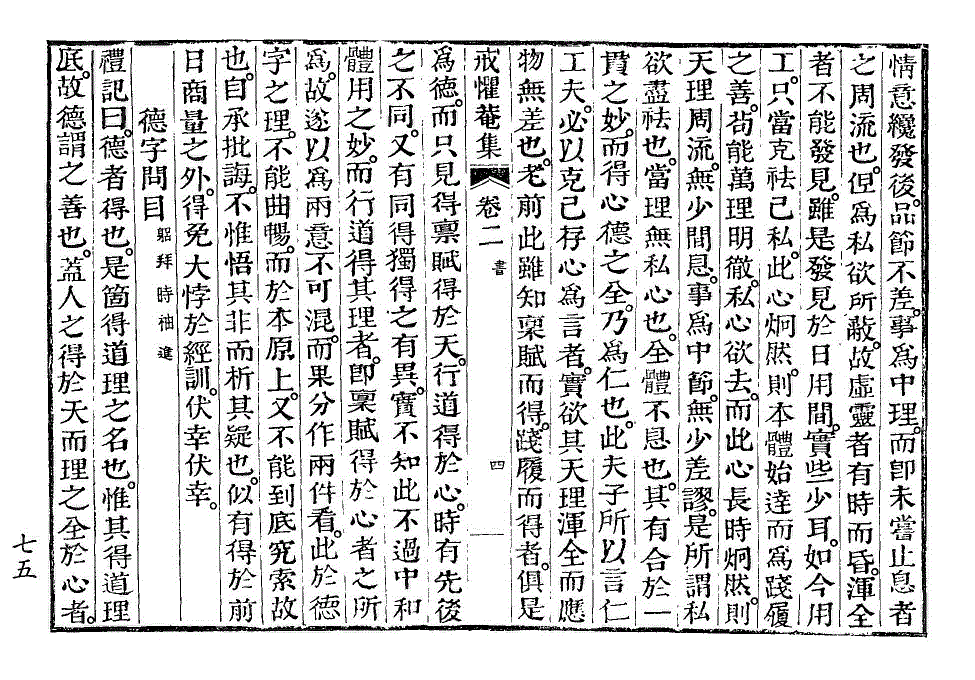 情意才发后。品节不差。事为中理。而即未尝止息者之周流也。但为私欲所蔽。故虚灵者有时而昏。浑全者不能发见。虽是发见于日用间。实些少耳。如今用工。只当克祛己私。此心炯然。则本体始达而为践履之善。苟能万理明彻。私心欲去。而此心长时炯然。则天理周流。无少间息。事为中节。无少差谬。是所谓私欲尽祛也。当理无私心也。全体不息也。其有合于一贯之妙。而得心德之全。乃为仁也。此夫子所以言仁工夫。必以克己存心为言者。实欲其天理浑全而应物无差也。老前此虽知禀赋而得。践履而得者。俱是为德。而只见得禀赋得于天。行道得于心。时有先后之不同。又有同得独得之有异。实不知此不过中和体用之妙。而行道得其理者。即禀赋得于心者之所为。故遂以为两意不可混。而果分作两件看。此于德字之理。不能曲畅。而于本原上。又不能到底究索故也。自承批诲。不惟悟其非而析其疑也。似有得于前日商量之外。得免大悖于经训。伏幸伏幸。
情意才发后。品节不差。事为中理。而即未尝止息者之周流也。但为私欲所蔽。故虚灵者有时而昏。浑全者不能发见。虽是发见于日用间。实些少耳。如今用工。只当克祛己私。此心炯然。则本体始达而为践履之善。苟能万理明彻。私心欲去。而此心长时炯然。则天理周流。无少间息。事为中节。无少差谬。是所谓私欲尽祛也。当理无私心也。全体不息也。其有合于一贯之妙。而得心德之全。乃为仁也。此夫子所以言仁工夫。必以克己存心为言者。实欲其天理浑全而应物无差也。老前此虽知禀赋而得。践履而得者。俱是为德。而只见得禀赋得于天。行道得于心。时有先后之不同。又有同得独得之有异。实不知此不过中和体用之妙。而行道得其理者。即禀赋得于心者之所为。故遂以为两意不可混。而果分作两件看。此于德字之理。不能曲畅。而于本原上。又不能到底究索故也。自承批诲。不惟悟其非而析其疑也。似有得于前日商量之外。得免大悖于经训。伏幸伏幸。德字问目(躬拜时袖进)
礼记曰。德者得也。是个得道理之名也。惟其得道理底。故德谓之善也。盖人之得于天而理之全于心者。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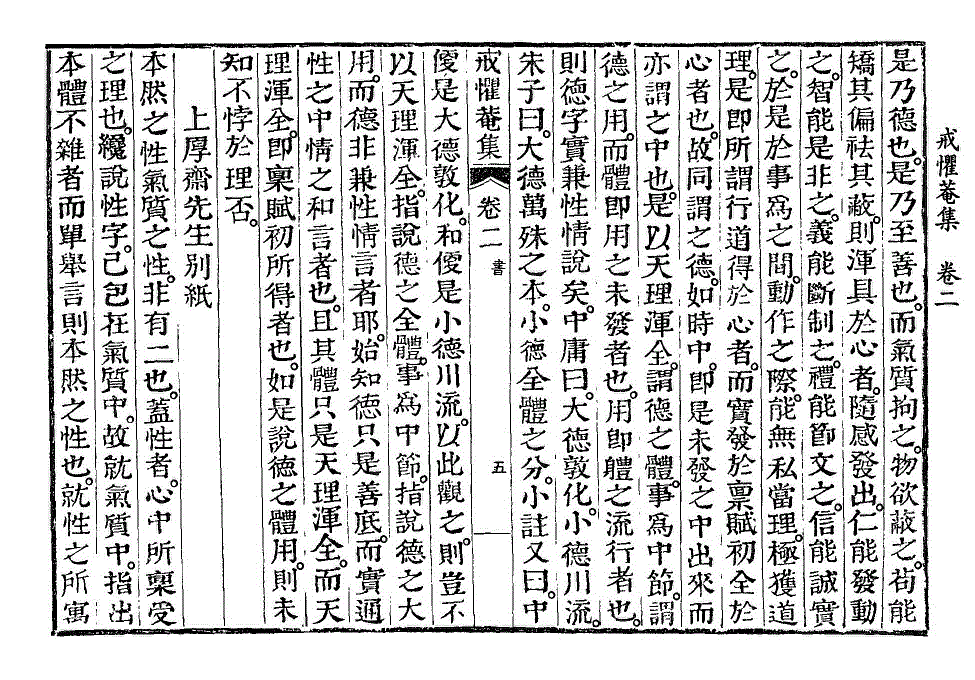 是乃德也。是乃至善也。而气质拘之。物欲蔽之。苟能矫其偏祛其蔽。则浑具于心者。随感发出。仁能发动之。智能是非之。义能断制之。礼能节文之。信能诚实之。于是于事为之间。动作之际。能无私当理。极获道理。是即所谓行道得于心者。而实发于禀赋初全于心者也。故同谓之德。如时中。即是未发之中出来而亦谓之中也。是以天理浑全。谓德之体。事为中节。谓德之用。而体即用之未发者也。用即体之流行者也。则德字实兼性情说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朱子曰。大德万殊之本。小德全体之分。小注又曰。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以此观之。则岂不以天理浑全。指说德之全体。事为中节。指说德之大用。而德非兼性情言者耶。始知德只是善底。而实通性之中情之和言者也。且其体只是天理浑全。而天理浑全。即禀赋初所得者也。如是说德之体用。则未知不悖于理否。
是乃德也。是乃至善也。而气质拘之。物欲蔽之。苟能矫其偏祛其蔽。则浑具于心者。随感发出。仁能发动之。智能是非之。义能断制之。礼能节文之。信能诚实之。于是于事为之间。动作之际。能无私当理。极获道理。是即所谓行道得于心者。而实发于禀赋初全于心者也。故同谓之德。如时中。即是未发之中出来而亦谓之中也。是以天理浑全。谓德之体。事为中节。谓德之用。而体即用之未发者也。用即体之流行者也。则德字实兼性情说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朱子曰。大德万殊之本。小德全体之分。小注又曰。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以此观之。则岂不以天理浑全。指说德之全体。事为中节。指说德之大用。而德非兼性情言者耶。始知德只是善底。而实通性之中情之和言者也。且其体只是天理浑全。而天理浑全。即禀赋初所得者也。如是说德之体用。则未知不悖于理否。上厚斋先生别纸
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非有二也。盖性者。心中所禀受之理也。才说性字。已包在气质中。故就气质中。指出本体不杂者而单举言则本然之性也。就性之所寓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6L 页
 处。不为除置而夹带言则气质之性也。是以本然之性气质之性。虽尧舜桀纣。人物禽兽。无不皆有。而所谓气质性云者。犹言气质中之性。非言气质亦是性也。然本然之性。只是一个至善底。气质之性。则有万不同。其所以本是一个善底。而终乃有万不同者。非元初禀受者。后来变幻也。特以气质有异。故其发用处。不无过不及之偏。此所以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有或不同。而其本体则只是依旧样在里面也。或者不知此义。有云气质之性与本然性有二。又有不知性只是理。而以为气质亦是禀受底物事。乃谓气质亦是性也。又有不知气质之性。亦有善底。如生知安行之资。即是气质性之善者。而以为气质性全是不善。乃云尧舜则无气质之性。又有知两性字本非二性。而以为或有偏驳之异者。特其本然之性。为气质所混。变其本体。做个不善故耳。其以本然气质谓是二性者。其说固不足深卞。而至若气质亦是性之说。尧舜则无气质性之说。本然性为气质所混。变其本体之说。此三者虽若似矣。而大有不然者矣。且或者有云气质性其体。即是本然之性。而其或不善者。特以气质有异。发用有偏。发用处便是气质之性也。遂
处。不为除置而夹带言则气质之性也。是以本然之性气质之性。虽尧舜桀纣。人物禽兽。无不皆有。而所谓气质性云者。犹言气质中之性。非言气质亦是性也。然本然之性。只是一个至善底。气质之性。则有万不同。其所以本是一个善底。而终乃有万不同者。非元初禀受者。后来变幻也。特以气质有异。故其发用处。不无过不及之偏。此所以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有或不同。而其本体则只是依旧样在里面也。或者不知此义。有云气质之性与本然性有二。又有不知性只是理。而以为气质亦是禀受底物事。乃谓气质亦是性也。又有不知气质之性。亦有善底。如生知安行之资。即是气质性之善者。而以为气质性全是不善。乃云尧舜则无气质之性。又有知两性字本非二性。而以为或有偏驳之异者。特其本然之性。为气质所混。变其本体。做个不善故耳。其以本然气质谓是二性者。其说固不足深卞。而至若气质亦是性之说。尧舜则无气质性之说。本然性为气质所混。变其本体之说。此三者虽若似矣。而大有不然者矣。且或者有云气质性其体。即是本然之性。而其或不善者。特以气质有异。发用有偏。发用处便是气质之性也。遂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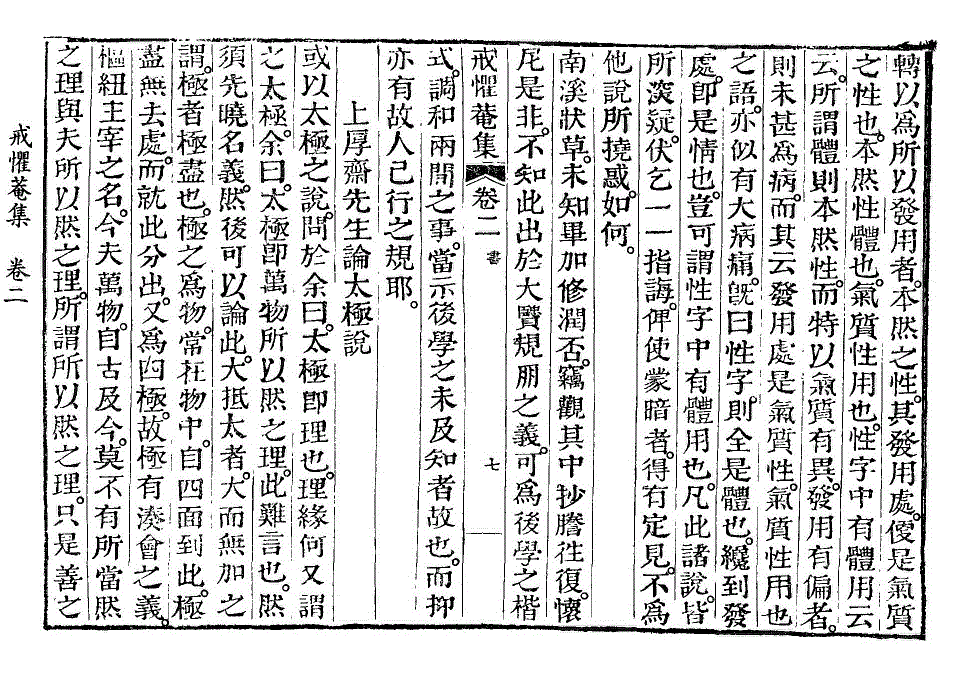 转以为所以发用者。本然之性。其发用处。便是气质之性也。本然性体也。气质性用也。性字中有体用云云。所谓体则本然性。而特以气质有异。发用有偏者。则未甚为病。而其云发用处是气质性。气质性用也之语。亦似有大病痛。既曰性字。则全是体也。才到发处。即是情也。岂可谓性字中有体用也。凡此诸说。皆所深疑。伏乞一一指诲。俾使蒙暗者。得有定见。不为他说所挠惑。如何。
转以为所以发用者。本然之性。其发用处。便是气质之性也。本然性体也。气质性用也。性字中有体用云云。所谓体则本然性。而特以气质有异。发用有偏者。则未甚为病。而其云发用处是气质性。气质性用也之语。亦似有大病痛。既曰性字。则全是体也。才到发处。即是情也。岂可谓性字中有体用也。凡此诸说。皆所深疑。伏乞一一指诲。俾使蒙暗者。得有定见。不为他说所挠惑。如何。南溪状草。未知毕加修润否。窃观其中抄誊往复。怀尼是非。不知此出于大贤规朋之义。可为后学之楷式。调和两间之事。当示后学之未及知者故也。而抑亦有故人已行之规耶。
上厚斋先生论太极说
或以太极之说。问于余曰。太极即理也。理缘何又谓之太极。余曰。太极即万物所以然之理。此难言也。然须先晓名义。然后可以论此。大抵太者。大而无加之谓。极者极尽也。极之为物。常在物中。自四面到此。极尽无去处。而就此分出。又为四极。故极有凑会之义。枢纽主宰之名。今夫万物。自古及今。莫不有所当然之理与夫所以然之理。所谓所以然之理。只是善之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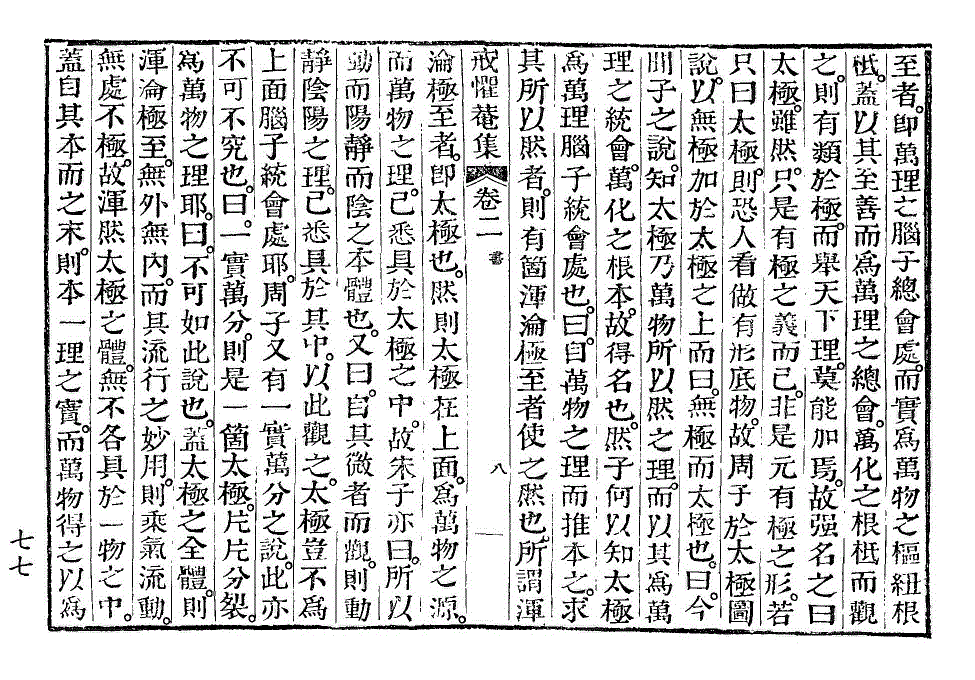 至者。即万理之脑子总会处。而实为万物之枢纽根柢。盖以其至善而为万理之总会。万化之根柢而观之。则有类于极。而举天下理。莫能加焉。故强名之曰太极。虽然。只是有极之义而已。非是元有极之形。若只曰太极。则恐人看做有形底物。故周子于太极图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而曰。无极而太极也。曰。今闻子之说。知太极乃万物所以然之理。而以其为万理之统会。万化之根本。故得名也。然子何以知太极为万理脑子统会处也。曰。自万物之理而推本之。求其所以然者。则有个浑沦极至者使之然也。所谓浑沦极至者。即太极也。然则太极在上面。为万物之源。而万物之理。已悉具于太极之中。故朱子亦曰。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又曰。自其微者而观。则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以此观之。太极岂不为上面脑子统会处耶。周子又有一实万分之说。此亦不可不究也。曰。一实万分。则是一个太极。片片分裂。为万物之理耶。曰。不可如此说也。盖太极之全体。则浑沦极至。无外无内。而其流行之妙用。则乘气流动。无处不极。故浑然太极之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盖自其本而之末。则本一理之实。而万物得之以为
至者。即万理之脑子总会处。而实为万物之枢纽根柢。盖以其至善而为万理之总会。万化之根柢而观之。则有类于极。而举天下理。莫能加焉。故强名之曰太极。虽然。只是有极之义而已。非是元有极之形。若只曰太极。则恐人看做有形底物。故周子于太极图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而曰。无极而太极也。曰。今闻子之说。知太极乃万物所以然之理。而以其为万理之统会。万化之根本。故得名也。然子何以知太极为万理脑子统会处也。曰。自万物之理而推本之。求其所以然者。则有个浑沦极至者使之然也。所谓浑沦极至者。即太极也。然则太极在上面。为万物之源。而万物之理。已悉具于太极之中。故朱子亦曰。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又曰。自其微者而观。则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以此观之。太极岂不为上面脑子统会处耶。周子又有一实万分之说。此亦不可不究也。曰。一实万分。则是一个太极。片片分裂。为万物之理耶。曰。不可如此说也。盖太极之全体。则浑沦极至。无外无内。而其流行之妙用。则乘气流动。无处不极。故浑然太极之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盖自其本而之末。则本一理之实。而万物得之以为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8H 页
 体者也。然以其浑沦者而观之。则天地万物。既由是而出。而无界限之别。只是依旧浑沦之本体而已。精粗本末。无彼此之间。故朱子有月映万川之譬而曰。分者不是割成片片去。陈北溪亦有水银之说。又何疑于片片分裂也哉。虽然。太极之流行在万物中者。此其当然者也。若只说太极。则为万理之统会而在于阴阳之先也。曰。然则太极在阴阳未生之前。兀然悬空独立乎。曰非也。盖自太极而观之。则冲漠无眹。统括万善。而使天下之理。莫不由是而出。以此观之。则太极似乎先阴阳。故言之而亦非离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是以必分开阴阳说。阳之前。阳之理先有。阴之前。阴之理先有则可也。若合阴阳而齐头说。阴阳未生之前。太极先有。不惟阴阳俱无未生时。太极亦不免。如子所谓悬空独立。是不成义理矣。曰。阳之前。阳之理先有。则在于何处。阴之前。阴之理先有。则在于何处。曰阳之前。阳之理在于阴。阴之前。阴之理在于阳。盖气则万殊而理则一也。气有先后而理无先后。故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阳之时。阴则未生。然所以为阴之理。即阳中所具之理。阴之时。阳则未生。然所以为
体者也。然以其浑沦者而观之。则天地万物。既由是而出。而无界限之别。只是依旧浑沦之本体而已。精粗本末。无彼此之间。故朱子有月映万川之譬而曰。分者不是割成片片去。陈北溪亦有水银之说。又何疑于片片分裂也哉。虽然。太极之流行在万物中者。此其当然者也。若只说太极。则为万理之统会而在于阴阳之先也。曰。然则太极在阴阳未生之前。兀然悬空独立乎。曰非也。盖自太极而观之。则冲漠无眹。统括万善。而使天下之理。莫不由是而出。以此观之。则太极似乎先阴阳。故言之而亦非离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是以必分开阴阳说。阳之前。阳之理先有。阴之前。阴之理先有则可也。若合阴阳而齐头说。阴阳未生之前。太极先有。不惟阴阳俱无未生时。太极亦不免。如子所谓悬空独立。是不成义理矣。曰。阳之前。阳之理先有。则在于何处。阴之前。阴之理先有。则在于何处。曰阳之前。阳之理在于阴。阴之前。阴之理在于阳。盖气则万殊而理则一也。气有先后而理无先后。故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阳之时。阴则未生。然所以为阴之理。即阳中所具之理。阴之时。阳则未生。然所以为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8L 页
 阳之理。即阴中所具之理。如人心之理。为万事之太极。天地之理。即人物之太极。先天地之理。为后天地之太极。后天地之理。为又后天地之太极。自上面引下来。没尽处。自下面推上去。没尽处。程子所以言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是以朱子曰。必欲推气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黄勉斋曰。理无迹而气有形。理无际而气有限。理一本而气万殊。故言理之当先乎气。深思之则无不通也。陈北溪曰。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蔡节斋曰。主太极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先。主阴阳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内。时既不同。所主皆异。不可执一而废一也。盖自阴阳未生之时而言。则所谓太极者。即在乎阴阳之中也。旨哉言乎。推此数说。则庶乎其通矣。(先生再三览毕曰。向以无极之极。为形之极时。大段迂阔。即今则涣然开悟。其间必大段用工矣。可喜可喜。)
阳之理。即阴中所具之理。如人心之理。为万事之太极。天地之理。即人物之太极。先天地之理。为后天地之太极。后天地之理。为又后天地之太极。自上面引下来。没尽处。自下面推上去。没尽处。程子所以言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是以朱子曰。必欲推气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黄勉斋曰。理无迹而气有形。理无际而气有限。理一本而气万殊。故言理之当先乎气。深思之则无不通也。陈北溪曰。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蔡节斋曰。主太极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先。主阴阳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内。时既不同。所主皆异。不可执一而废一也。盖自阴阳未生之时而言。则所谓太极者。即在乎阴阳之中也。旨哉言乎。推此数说。则庶乎其通矣。(先生再三览毕曰。向以无极之极。为形之极时。大段迂阔。即今则涣然开悟。其间必大段用工矣。可喜可喜。)上厚斋先生
近于病里。究看牛,栗理气长书。其为说殊极详备。无有馀蕴。苟得涵泳。庶可洞见。大抵人心道心。则或可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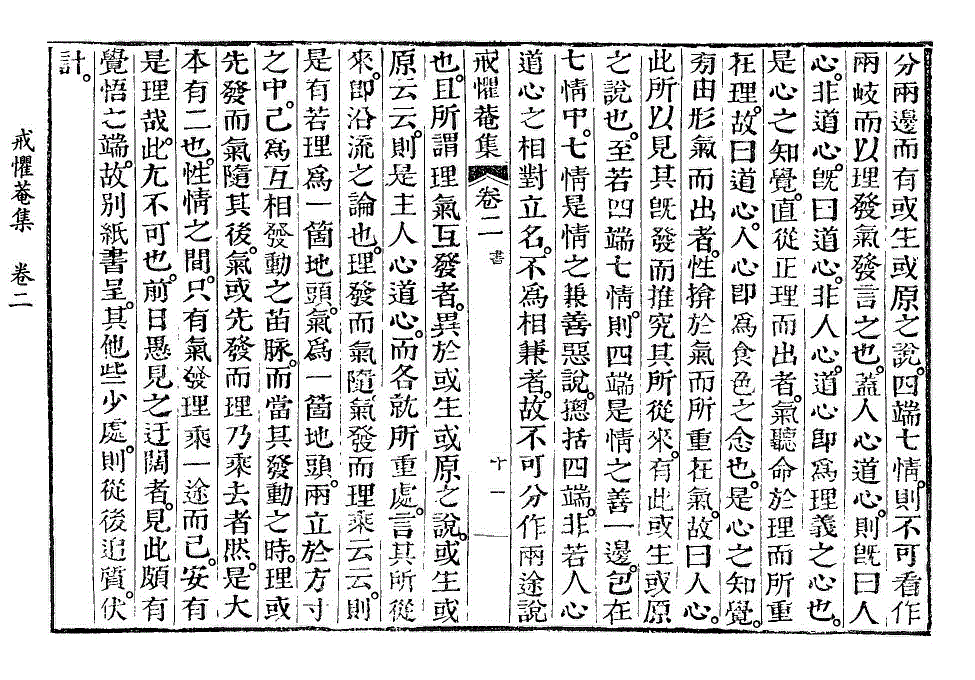 分两边而有或生或原之说。四端七情。则不可看作两岐而以理发气发言之也。盖人心道心。则既曰人心。非道心。既曰道心。非人心。道心即为理义之心也。是心之知觉。直从正理而出者。气听命于理而所重在理。故曰道心。人心即为食色之念也。是心之知觉。旁由形气而出者。性掩于气而所重在气。故曰人心。此所以见其既发而推究其所从来。有此或生或原之说也。至若四端七情。则四端是情之善一边。包在七情中。七情是情之兼善恶说。总括四端。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对立名。不为相兼者。故不可分作两途说也。且所谓理气互发者。异于或生或原之说。或生或原云云。则是主人心道心。而各就所重处。言其所从来。即沿流之论也。理发而气随。气发而理乘云云。则是有若理为一个地头。气为一个地头。两立于方寸之中。已为互相发动之苗脉。而当其发动之时。理或先发而气随其后。气或先发而理乃乘去者然。是大本有二也。性情之间。只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安有是理哉。此尤不可也。前日愚见之迂阔者。见此颇有觉悟之端。故别纸书呈。其他些少处。则从后追质。伏计。
分两边而有或生或原之说。四端七情。则不可看作两岐而以理发气发言之也。盖人心道心。则既曰人心。非道心。既曰道心。非人心。道心即为理义之心也。是心之知觉。直从正理而出者。气听命于理而所重在理。故曰道心。人心即为食色之念也。是心之知觉。旁由形气而出者。性掩于气而所重在气。故曰人心。此所以见其既发而推究其所从来。有此或生或原之说也。至若四端七情。则四端是情之善一边。包在七情中。七情是情之兼善恶说。总括四端。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对立名。不为相兼者。故不可分作两途说也。且所谓理气互发者。异于或生或原之说。或生或原云云。则是主人心道心。而各就所重处。言其所从来。即沿流之论也。理发而气随。气发而理乘云云。则是有若理为一个地头。气为一个地头。两立于方寸之中。已为互相发动之苗脉。而当其发动之时。理或先发而气随其后。气或先发而理乃乘去者然。是大本有二也。性情之间。只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安有是理哉。此尤不可也。前日愚见之迂阔者。见此颇有觉悟之端。故别纸书呈。其他些少处。则从后追质。伏计。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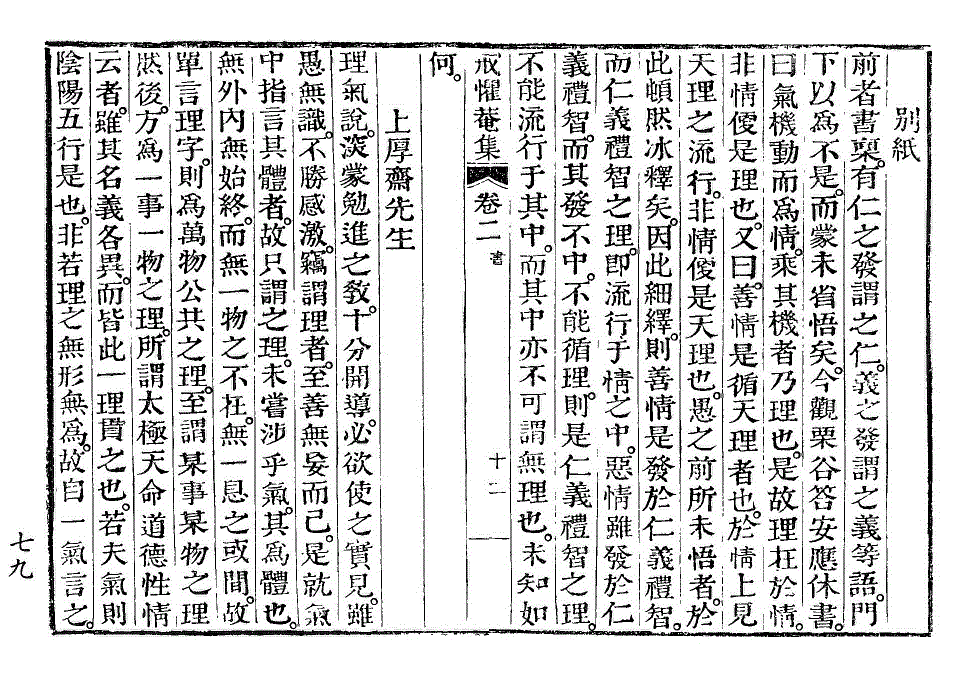 别纸
别纸前者书禀。有仁之发谓之仁。义之发谓之义等语。门下以为不是。而蒙未省悟矣。今观栗谷答安应休书。曰气机动而为情。乘其机者乃理也。是故理在于情。非情便是理也。又曰。善情是循天理者也。于情上见天理之流行。非情便是天理也。愚之前所未悟者。于此顿然冰释矣。因此细绎。则善情是发于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之理。即流行于情之中。恶情虽发于仁义礼智。而其发不中。不能循理。则是仁义礼智之理。不能流行于其中。而其中亦不可谓无理也。未知如何。
上厚斋先生
理气说。深蒙勉进之教。十分开导。必欲使之实见。虽愚无识。不胜感激。窃谓理者。至善无妄而已。是就气中指言其体者。故只谓之理。未尝涉乎气。其为体也。无外内无始终。而无一物之不在。无一息之或间。故单言理字。则为万物公共之理。至谓某事某物之理然后。方为一事一物之理。所谓太极天命道德性情云者。虽其名义各异。而皆此一理贯之也。若夫气则阴阳五行是也。非若理之无形无为。故自一气言之。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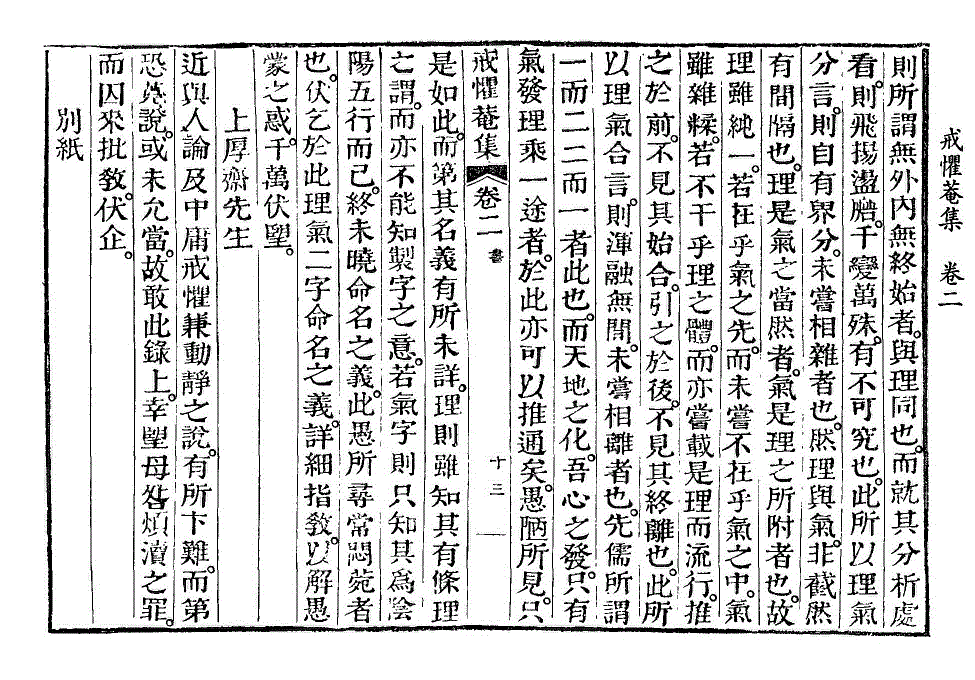 则所谓无外内无终始者。与理同也。而就其分析处看。则飞扬荡磨。千变万殊。有不可究也。此所以理气分言。则自有界分。未尝相杂者也。然理与气。非截然有间隔也。理是气之当然者。气是理之所附者也。故理虽纯一。若在乎气之先。而未尝不在乎气之中。气虽杂糅。若不干乎理之体。而亦尝载是理而流行。推之于前。不见其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离也。此所以理气合言。则浑融无间。未尝相离者也。先儒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此也。而天地之化。吾心之发。只有气发理乘一途者。于此亦可以推通矣。愚陋所见。只是如此。而第其名义有所未详。理则虽知其有条理之谓。而亦不能知制字之意。若气字则只知其为阴阳五行而已。终未晓命名之义。此愚所寻常闷菀者也。伏乞于此理气二字命名之义。详细指教。以解愚蒙之惑。千万伏望。
则所谓无外内无终始者。与理同也。而就其分析处看。则飞扬荡磨。千变万殊。有不可究也。此所以理气分言。则自有界分。未尝相杂者也。然理与气。非截然有间隔也。理是气之当然者。气是理之所附者也。故理虽纯一。若在乎气之先。而未尝不在乎气之中。气虽杂糅。若不干乎理之体。而亦尝载是理而流行。推之于前。不见其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离也。此所以理气合言。则浑融无间。未尝相离者也。先儒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此也。而天地之化。吾心之发。只有气发理乘一途者。于此亦可以推通矣。愚陋所见。只是如此。而第其名义有所未详。理则虽知其有条理之谓。而亦不能知制字之意。若气字则只知其为阴阳五行而已。终未晓命名之义。此愚所寻常闷菀者也。伏乞于此理气二字命名之义。详细指教。以解愚蒙之惑。千万伏望。上厚斋先生
近与人论及中庸戒惧兼动静之说。有所卞难。而第恐荛说。或未允当。故敢此录上。幸望毋咎烦渎之罪。而囚来批教。伏企。
别纸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0L 页
 戒惧是存养于未发时工夫。谨独是省察于已发后工夫。若以戒惧谓兼动静则恐未然。
戒惧是存养于未发时工夫。谨独是省察于已发后工夫。若以戒惧谓兼动静则恐未然。(右衡老说)
戒惧是兼动静说。谨独是专言动时。不睹不闻。虽是未发境界。而承上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之语说来。则只作静时工夫看不得。窃详此节之意。盖云道是不可须臾离底。若是可离。非道也。故虽在不睹不闻之中。亦必戒慎恐惧。使体立而用行。欲其无顷刻之离道也。章句中虽字亦字。最宜着力看。下文慎独。则是善恶几所由分。尤当加意着工处也。故又复提说来。朱子答胡季随书。说得分晓。可考。故录在下方。
大抵其言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是故君子戒惧不睹。恐惧不闻。乃是彻头彻尾。无时无处。不下工夫。欲其无须臾而离乎道也。又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乃是上文全体工夫之中。见得此处是一念起处。又更紧切。故当于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隐而见。自微而显。皆无人欲之私也。(朱书删节右即或人答说)
戒惧固是承道不可须臾离说来。盖此节之意。犹言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1H 页
 道体广大悠久。不可须臾离失。故君子虽须臾之顷。亦尝戒惧也。(不睹不闻。即耳目之所不及。是释须臾之意。)夫既曰虽须臾之顷。亦尝戒惧。则其动时敬谨之意。在于言外。故朱子亦有彻头彻尾无时无处不下工夫等说话。以此泛观。则戒惧似若通贯动静。然但以下文谨独对看。而寻其着工意味。则戒惧是略略收拾。谨独是尤加省谨。故当其未发。固戒谨。而及其发也。只谨独而已。不可谓戒惧谨独。夹杂并行于已发之际。则向者朱书所谓无时无处不下工夫之中。谨独亦已包在。而戒惧实非兼动静矣。是以朱子曰。戒惧防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将然。以审其几。又曰。戒惧静工夫。谨独动工夫。今以戒惧兼动静之说观之。则是戒惧谨独。夹杂并行于已发之际。岂不重复碍滞而有违于朱子之说耶。大抵戒惧单言则该动静。而对谨独而言。则各有归属。自成两事。以本文言之。初言道之出于天备于己。次两节。分言存养省察之要。次言性情体用之别。终言存养省察之效。其分对待。各有归属者明矣。若曰戒惧兼动静。则恐非中庸本文之旨也。
道体广大悠久。不可须臾离失。故君子虽须臾之顷。亦尝戒惧也。(不睹不闻。即耳目之所不及。是释须臾之意。)夫既曰虽须臾之顷。亦尝戒惧。则其动时敬谨之意。在于言外。故朱子亦有彻头彻尾无时无处不下工夫等说话。以此泛观。则戒惧似若通贯动静。然但以下文谨独对看。而寻其着工意味。则戒惧是略略收拾。谨独是尤加省谨。故当其未发。固戒谨。而及其发也。只谨独而已。不可谓戒惧谨独。夹杂并行于已发之际。则向者朱书所谓无时无处不下工夫之中。谨独亦已包在。而戒惧实非兼动静矣。是以朱子曰。戒惧防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将然。以审其几。又曰。戒惧静工夫。谨独动工夫。今以戒惧兼动静之说观之。则是戒惧谨独。夹杂并行于已发之际。岂不重复碍滞而有违于朱子之说耶。大抵戒惧单言则该动静。而对谨独而言。则各有归属。自成两事。以本文言之。初言道之出于天备于己。次两节。分言存养省察之要。次言性情体用之别。终言存养省察之效。其分对待。各有归属者明矣。若曰戒惧兼动静。则恐非中庸本文之旨也。(右又衡老说)
上厚斋先生
谨独说。蒙此满纸缕缕。赐诲勤勤。翘望之馀。不任感喜。所谓或人。即李都事度远也。就达未发若以其体言之。则即性也。大本也。是个率性之道。而流行日用之间者。固不可谓拘于一时。限于一处。然若以未发时节言之。则即事物未接。思虑未萌之时。自与已发之时。相为先后。有若冬先于春。春后于冬者。故先儒有只言未发二字处。有言未发之时处。窃恐只言未发二字处。则当看作未发之体。言未发之时处。则当看作事物未接思虑未萌之时。以此看。未知如何。
上厚斋先生
朱子曰。廓然大公。是寂然不动也。物来顺应。是感而遂通也。夫寂然。未发之时也。专指静言。大公无私之谓。通贯动静言。于此何以打成一片说也。老尝自解曰。七情未发之前。心之全体。寂然湛然。此即天下之大本。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动者也。以此观之。寂然固是指未发言。然感应之际。此心莹然无私者。即动中之静。而所谓体用一原。流行不息者也。故朱子曰。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乃动中之静。而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又曰。胡文定所谓不起不灭。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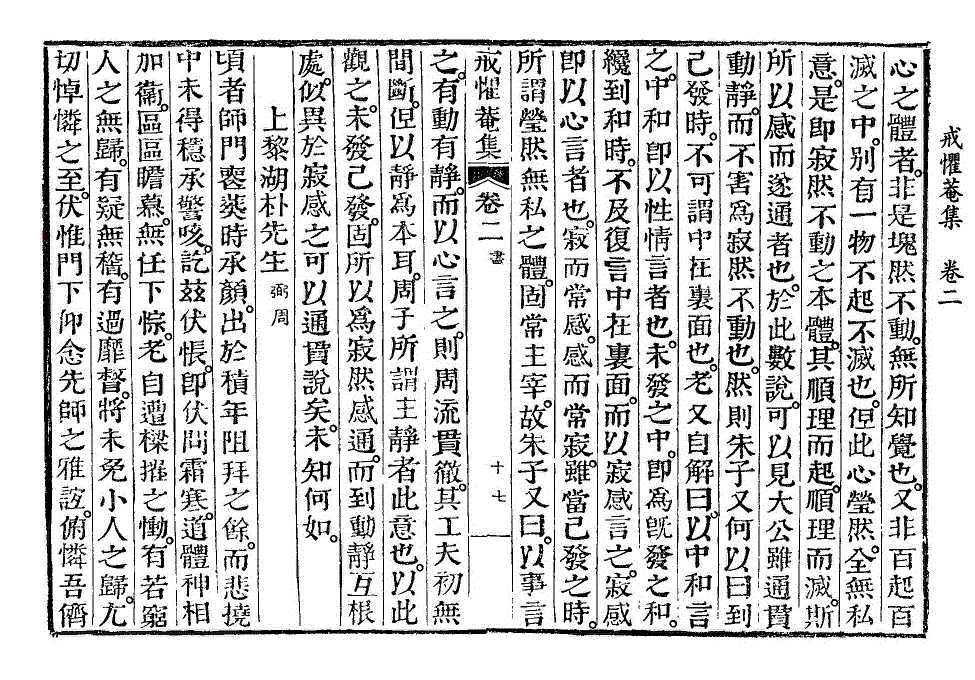 心之体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即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所以感而遂通者也。于此数说。可以见大公虽通贯动静。而不害为寂然不动也。然则朱子又何以曰到已发时。不可谓中在里面也。老又自解曰。以中和言之。中和即以性情言者也。未发之中。即为既发之和。才到和时。不及复言中在里面。而以寂感言之。寂感即以心言者也。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虽当已发之时。所谓莹然无私之体。固常主宰。故朱子又曰。以事言之。有动有静。而以心言之。则周流贯彻。其工夫初无间断。但以静为本耳。周子所谓主静者此意也。以此观之。未发已发。固所以为寂然感通。而到动静互根处。似异于寂感之可以通贯说矣。未知何如。
心之体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即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所以感而遂通者也。于此数说。可以见大公虽通贯动静。而不害为寂然不动也。然则朱子又何以曰到已发时。不可谓中在里面也。老又自解曰。以中和言之。中和即以性情言者也。未发之中。即为既发之和。才到和时。不及复言中在里面。而以寂感言之。寂感即以心言者也。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虽当已发之时。所谓莹然无私之体。固常主宰。故朱子又曰。以事言之。有动有静。而以心言之。则周流贯彻。其工夫初无间断。但以静为本耳。周子所谓主静者此意也。以此观之。未发已发。固所以为寂然感通。而到动静互根处。似异于寂感之可以通贯说矣。未知何如。上黎湖朴先生(弼周)
顷者师门丧葬时承颜。出于积年阻拜之馀。而悲挠中未得稳承警咳。讫玆伏怅。即伏问霜寒。道体神相加卫。区区瞻慕。无任下悰。老自遭梁摧之恸。有若穷人之无归。有疑无稽。有过靡督。将未免小人之归。尤切悼怜之至。伏惟门下仰念先师之雅谊。俯怜吾侪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2L 页
 之靡依。其所矜诲。想无异于程子之视东方诸人。向慕就正之心。玆倍于它日矣。窃有疑义。别纸录呈。伏乞特怜蒙感。俯赐批教。俾使愚昧得以披雾。千万伏望。
之靡依。其所矜诲。想无异于程子之视东方诸人。向慕就正之心。玆倍于它日矣。窃有疑义。别纸录呈。伏乞特怜蒙感。俯赐批教。俾使愚昧得以披雾。千万伏望。别纸
祭祀祖考来格之理。程子亦谓当置(缺)之间。则此非蒙学之所敢轻议。而谨按祭义曰。致斋于内。散斋于外。斋之日。思其居处笑语志意嗜乐。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僾然必有见乎其位。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慨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又按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窃谓来格云者。非谓祖考之神。常在虚空之中。而祭祀之时。方降格也。即此祭者之心。僾然如在者。便是来格也。然则祖考之来格与否。只在祭者之诚敬有无。范氏所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谢氏所谓子孙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者。良以此也。如此看得。未审是否。伏乞批教。
葬礼赠置柩东侧之说。此是老先生晚年之言。非惟韩友师朝有所受。老亦尝有所闻。而顷当师门窆时。门下所教赠置柩上东边之说。亦有所据。故主家从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3H 页
 之。然其后闻金宁海外孙尹进士暹之言。则宁海丈葬时。老先生主丧。而亦行柩东侧之礼矣。故窃取家礼而更考之。则所谓奉置柩旁四字。已是大煞分明。无可疑者矣。何则。家礼中多般旁字。如深衣章裳之右旁之旁字。治葬章穿圹条旁穿土室之旁字。四旁旋下四物之旁字。作主条窍其旁之旁字。发引条主人兄弟皆宿柩旁之旁字。皆以旁侧之义言。则此所谓柩旁二字。岂非指柩之东侧而言耶。惟题主条其下左旁之旁字。虽就粉面上说。而所谓其字。非通主身言。乃单指粉面说。不曰主旁。而必曰其下左旁。以明其涂粉处之左旁。则其立文下语。岂不详密耶。主人赠。若置柩上。则亦必曰柩上左旁。如其下左旁之例。而必不只曰柩旁而已也。且况开元礼奠于柩东之说。尤似较著。此柩东二字。亦与家礼大敛章设跗于柩东。设灵床于柩东及奔丧章柩东西向坐三个柩东之义同。亦岂非指柩之东侧说耶。但门下曰。奠安置也。若置于棺椁之狭隙则非安置也。或者又言玄六纁四。难容于棺椁之间。此似然矣。然谨按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注。此言阔狭之度。古者棺外椁内。皆有藏器。安有容壶容甒藏
之。然其后闻金宁海外孙尹进士暹之言。则宁海丈葬时。老先生主丧。而亦行柩东侧之礼矣。故窃取家礼而更考之。则所谓奉置柩旁四字。已是大煞分明。无可疑者矣。何则。家礼中多般旁字。如深衣章裳之右旁之旁字。治葬章穿圹条旁穿土室之旁字。四旁旋下四物之旁字。作主条窍其旁之旁字。发引条主人兄弟皆宿柩旁之旁字。皆以旁侧之义言。则此所谓柩旁二字。岂非指柩之东侧而言耶。惟题主条其下左旁之旁字。虽就粉面上说。而所谓其字。非通主身言。乃单指粉面说。不曰主旁。而必曰其下左旁。以明其涂粉处之左旁。则其立文下语。岂不详密耶。主人赠。若置柩上。则亦必曰柩上左旁。如其下左旁之例。而必不只曰柩旁而已也。且况开元礼奠于柩东之说。尤似较著。此柩东二字。亦与家礼大敛章设跗于柩东。设灵床于柩东及奔丧章柩东西向坐三个柩东之义同。亦岂非指柩之东侧说耶。但门下曰。奠安置也。若置于棺椁之狭隙则非安置也。或者又言玄六纁四。难容于棺椁之间。此似然矣。然谨按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注。此言阔狭之度。古者棺外椁内。皆有藏器。安有容壶容甒藏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3L 页
 器之处。不能安置玄纁之理也。家礼虽有椁堇能容棺之文。而其间似不至于如此之狭也。老既考此然后。始知师门已行之礼。果有考据。而窃恨其时未能以此数说。卞禀于门下也。虽然。看文之道。每有先入之见所主。或恐区区所引之说。有牵强穿凿之弊。兹敢仰质。伏乞怜其愚蒙。回赐批诲。千万至祝。
器之处。不能安置玄纁之理也。家礼虽有椁堇能容棺之文。而其间似不至于如此之狭也。老既考此然后。始知师门已行之礼。果有考据。而窃恨其时未能以此数说。卞禀于门下也。虽然。看文之道。每有先入之见所主。或恐区区所引之说。有牵强穿凿之弊。兹敢仰质。伏乞怜其愚蒙。回赐批诲。千万至祝。上黎湖先生
一息之地。周年阻候。是岂向慕之诚哉。伏不审腊寒。静养道体神相万安。门下日者登对。明大义格 君心。大君子事业。可以有传于天下后世。其为吾道之光。迥出万万。区区瞻仰之怀。愈久而愈不已也。准拟一者趋谒。而病故连仍。久未遂计。愧叹之忱。惟日积于中矣。兹敢专伻。仰候动静。
上陶庵先生
衡老之始谒门下。计今五载。初既卒卒承颜。而私故缠掣。足迹不复及门。又不能奉书时候动静。则门下亦安能记其为何许人也。反躬循省。深愧其摧颓庸愚。而区区瞻慕。惟日积于中矣。霜飙渐紧。伏未审道体神相万安。尤不任瞻慕下诚。窃伏念老癃废昏懦。无可言者。但读书求志。就正有道。乃平生宿愿。而中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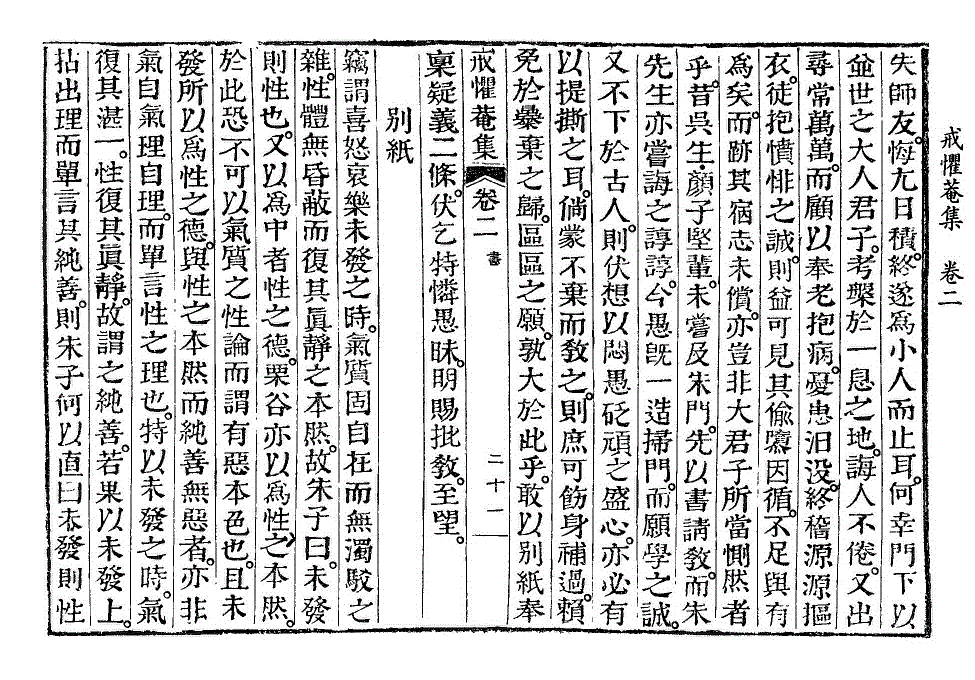 失师友。悔尤日积。终遂为小人而止耳。何幸门下以并世之大人君子。考槃于一息之地。诲人不倦。又出寻常万万。而顾以奉老抱病。忧患汨没。终稽源源抠衣。徒抱愤悱之诚。则益可见其偷隳因循。不足与有为矣。而迹其宿志未偿。亦岂非大君子所当恻然者乎。昔吴生,颜子坚辈。未尝及朱门。先以书请教。而朱先生亦尝诲之谆谆。今愚既一造扫门。而愿学之诚。又不下于古人。则伏想以闷愚砭顽之盛心。亦必有以提撕之耳。倘蒙不弃而教之。则庶可饬身补过。赖免于㬥弃之归。区区之愿。孰大于此乎。敢以别纸奉禀疑义二条。伏乞特怜愚昧。明赐批教。至望。
失师友。悔尤日积。终遂为小人而止耳。何幸门下以并世之大人君子。考槃于一息之地。诲人不倦。又出寻常万万。而顾以奉老抱病。忧患汨没。终稽源源抠衣。徒抱愤悱之诚。则益可见其偷隳因循。不足与有为矣。而迹其宿志未偿。亦岂非大君子所当恻然者乎。昔吴生,颜子坚辈。未尝及朱门。先以书请教。而朱先生亦尝诲之谆谆。今愚既一造扫门。而愿学之诚。又不下于古人。则伏想以闷愚砭顽之盛心。亦必有以提撕之耳。倘蒙不弃而教之。则庶可饬身补过。赖免于㬥弃之归。区区之愿。孰大于此乎。敢以别纸奉禀疑义二条。伏乞特怜愚昧。明赐批教。至望。别纸
窃谓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质固自在而无浊驳之杂。性体无昏蔽而复其真静之本然。故朱子曰。未发则性也。又以为中者性之德。栗谷亦以为性之本然。于此恐不可以气质之性论而谓有恶本色也。且未发所以为性之德。与性之本然而纯善无恶者。亦非气自气理自理。而单言性之理也。特以未发之时。气复其湛一。性复其真静。故谓之纯善。若果以未发上。拈出理而单言其纯善。则朱子何以直曰未发则性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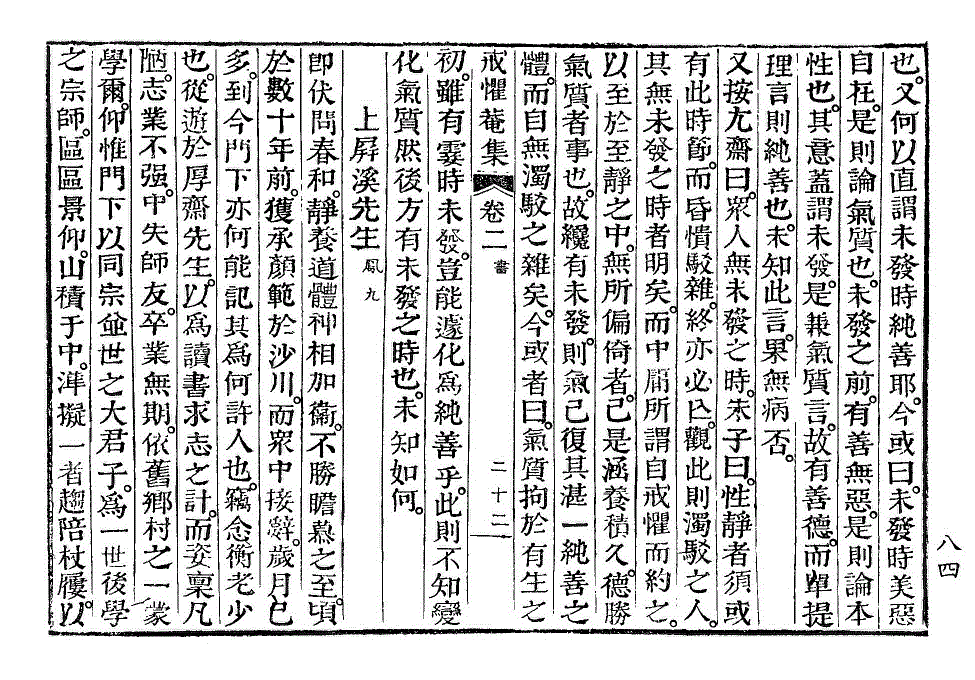 也。又何以直谓未发时纯善耶。今或曰。未发时美恶自在。是则论气质也。未发之前。有善无恶。是则论本性也。其意盖谓未发。是兼气质言。故有善德。而单提理言则纯善也。未知此言。果无病否。
也。又何以直谓未发时纯善耶。今或曰。未发时美恶自在。是则论气质也。未发之前。有善无恶。是则论本性也。其意盖谓未发。是兼气质言。故有善德。而单提理言则纯善也。未知此言。果无病否。又按尤斋曰。众人无未发之时。朱子曰。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而昏愦驳杂。终亦必亡。观此则浊驳之人。其无未发之时者明矣。而中庸所谓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者。已是涵养积久。德胜气质者事也。故才有未发。则气已复其湛一纯善之体。而自无浊驳之杂矣。今或者曰。气质拘于有生之初。虽有霎时未发。岂能遽化为纯善乎。此则不知变化气质然后方有未发之时也。未知如何。
上屏溪先生(凤九)
即伏问春和。静养道体神相加卫。不胜瞻慕之至。顷于数十年前。获承颜范于沙川。而众中接辞。岁月已多。到今门下亦何能记其为何许人也。窃念衡老少也。从游于厚斋先生。以为读书求志之计。而姿禀凡陋。志业不强。中失师友。卒业无期。依旧乡村之一蒙学尔。仰惟门下以同宗并世之大君子。为一世后学之宗师。区区景仰。山积于中。准拟一者趋陪杖屦。以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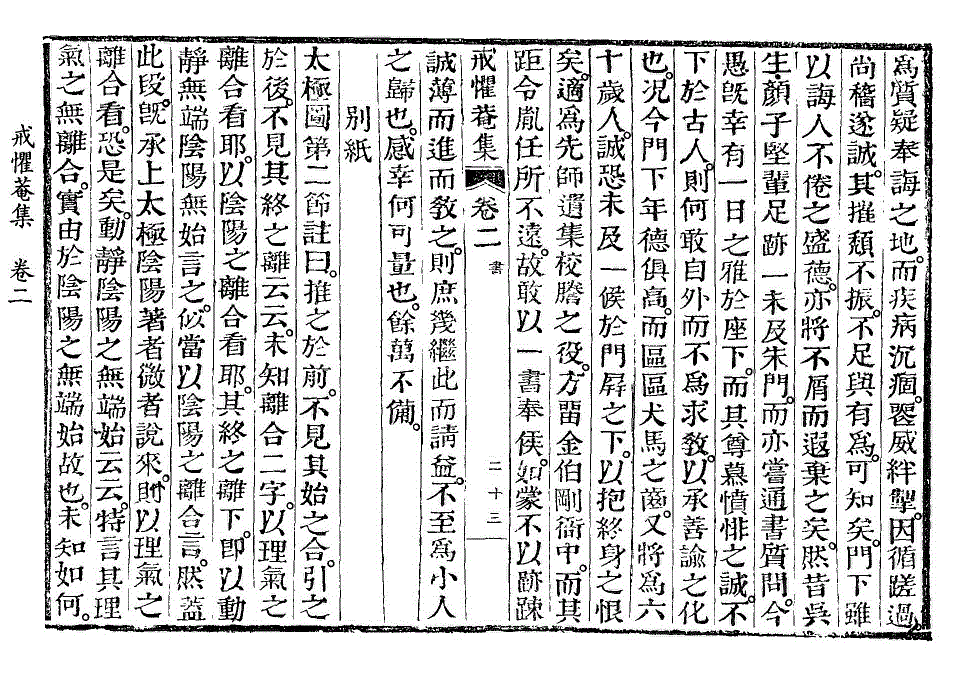 为质疑奉诲之地。而疾病沉痼。丧威绊掣。因循蹉过。尚稽遂诚。其摧颓不振。不足与有为。可知矣。门下虽以诲人不倦之盛德。亦将不屑而遐弃之矣。然昔吴生,颜子坚辈足迹一未及朱门。而亦尝通书质问。今愚既幸有一日之雅于座下。而其尊慕愤悱之诚。不下于古人。则何敢自外而不为求教。以承善谕之化也。况今门下年德俱高。而区区犬马之齿。又将为六十岁人。诚恐未及一候于门屏之下。以抱终身之恨矣。适为先师遗集校誊之役。方留金伯刚衙中。而其距令胤任所不远。故敢以一书奉候。如蒙不以迹疏诚薄而进而教之。则庶几继此而请益。不至为小人之归也。感幸何可量也。馀万不备。
为质疑奉诲之地。而疾病沉痼。丧威绊掣。因循蹉过。尚稽遂诚。其摧颓不振。不足与有为。可知矣。门下虽以诲人不倦之盛德。亦将不屑而遐弃之矣。然昔吴生,颜子坚辈足迹一未及朱门。而亦尝通书质问。今愚既幸有一日之雅于座下。而其尊慕愤悱之诚。不下于古人。则何敢自外而不为求教。以承善谕之化也。况今门下年德俱高。而区区犬马之齿。又将为六十岁人。诚恐未及一候于门屏之下。以抱终身之恨矣。适为先师遗集校誊之役。方留金伯刚衙中。而其距令胤任所不远。故敢以一书奉候。如蒙不以迹疏诚薄而进而教之。则庶几继此而请益。不至为小人之归也。感幸何可量也。馀万不备。别纸
太极图第二节注曰。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云云。未知离合二字。以理气之离合看耶。以阴阳之离合看耶。其终之离下。即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言之。似当以阴阳之离合言。然盖此段。既承上太极阴阳著者微者说来。则以理气之离合看。恐是矣。动静阴阳之无端始云云。特言其理气之无离合。实由于阴阳之无端始故也。未知如何。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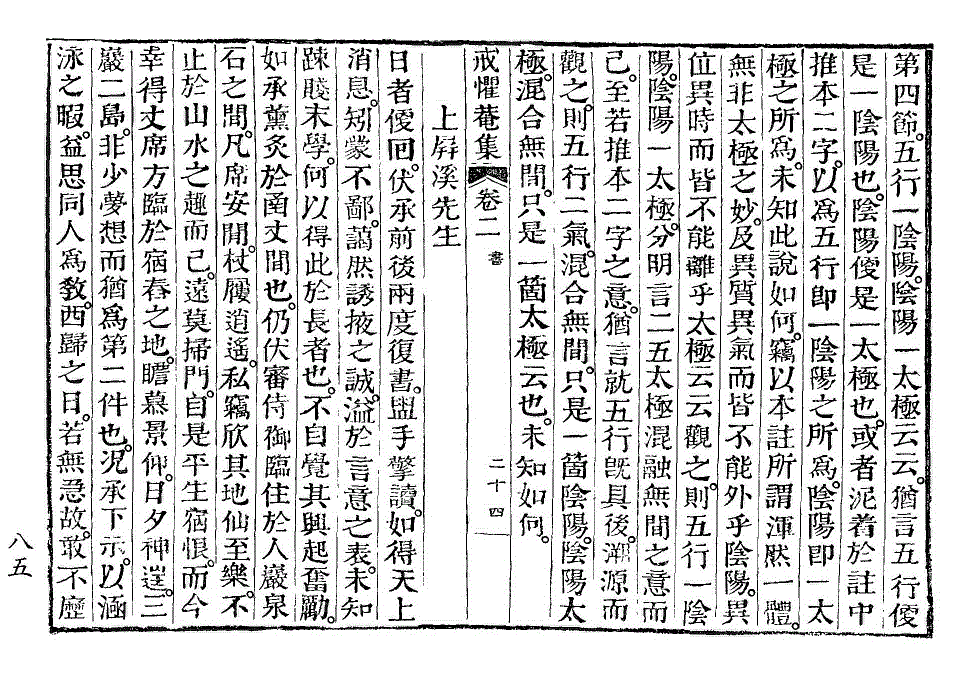 第四节。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云云。犹言五行便是一阴阳也。阴阳便是一太极也。或者泥着于注中推本二字。以为五行即一阴阳之所为。阴阳即一太极之所为。未知此说如何。窃以本注所谓浑然一体。无非太极之妙。及异质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异位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云云观之。则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分明言二五太极混融无间之意而已。至若推本二字之意。犹言就五行既具后。溯源而观之。则五行二气。混合无间。只是一个阴阳。阴阳太极。混合无间。只是一个太极云也。未知如何。
第四节。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云云。犹言五行便是一阴阳也。阴阳便是一太极也。或者泥着于注中推本二字。以为五行即一阴阳之所为。阴阳即一太极之所为。未知此说如何。窃以本注所谓浑然一体。无非太极之妙。及异质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异位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云云观之。则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分明言二五太极混融无间之意而已。至若推本二字之意。犹言就五行既具后。溯源而观之。则五行二气。混合无间。只是一个阴阳。阴阳太极。混合无间。只是一个太极云也。未知如何。上屏溪先生
日者便回。伏承前后两度复书。盥手擎读。如得天上消息。矧蒙不鄙。蔼然诱掖之诚。溢于言意之表。未知疏贱末学。何以得此于长者也。不自觉其兴起奋励。如承薰炙于函丈间也。仍伏审侍御临住于人岩泉石之间。凡席安閒。杖屦逍遥。私窃欣其地仙至乐。不止于山水之趣而已。远莫扫门。自是平生宿恨。而今幸得丈席方临于宿舂之地。瞻慕景仰。日夕神𨓏。三岩二岛。非少梦想而犹为第二件也。况承下示。以涵泳之暇。益思同人为教。西归之日。若无急故。敢不历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6H 页
 拜于泉声岳色之中。稳承提耳之教也。别纸所禀。不以无似而斥之。猥蒙谆谆之诲。又许以继续讲质。窃谓倦勤之时。学不厌教不倦之盛意。未见若是勤恳也。区区不胜感且说也。
拜于泉声岳色之中。稳承提耳之教也。别纸所禀。不以无似而斥之。猥蒙谆谆之诲。又许以继续讲质。窃谓倦勤之时。学不厌教不倦之盛意。未见若是勤恳也。区区不胜感且说也。别纸
别纸所禀第一条。窃自幸瞽说之不悖于明鉴。而第二条说。愚滞之见。犹未能领悟于提撕之下。故冀蒙卒业之恩。又敢录禀。恐妨静摄。还切悚仄之至。窃谓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云云。下教以此段谓统说太极无乎不在之意。而理气混融无间之意。自在其中云云。区区于此。疑未释焉。何者。通书所谓一实万分会万为一一句语。其解此意。可谓八字打开矣。太极动而生阳。至四时行焉。是一实万分之意。此段五行一阴阳。至太极本无极。是会万为一之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又申言一实万分之意。会万为一。即二五太极浑然一体之意。一实万分。是太极无乎不在之义也。周子于此。恐人致疑于五殊二实之有馀欠而阴阳太极之有间隔。故又推本而总言之。以明理气浑然一体及理无不在之意。是故朱子于注。亦以此两仪对待说去。本段注所谓以明浑然一体莫非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6L 页
 无极之妙。及盖五行四时不外阴阳。止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云云。是释一阴阳一太极本无极之意也。无极之妙。未尝不各具及五行之生随其气质以下。是释五行各一性之意也。下大文注。统体一太极。语大莫能载。是应二五一太极言也。各具一太极。语小莫能破。是应五行各一性言也。上大文注结语所谓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夫岂有所亏欠间隔云云。所以先言此段之意。而与剥图解所言五殊二实无馀欠。精粗本末无彼此云云。皆所以明理气浑然一体之意也。如是看见。未知如何。非敢自信。不明不措。诚为请益之要。故更此烦禀。伏乞怜其愚昧。明赐批教。
无极之妙。及盖五行四时不外阴阳。止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云云。是释一阴阳一太极本无极之意也。无极之妙。未尝不各具及五行之生随其气质以下。是释五行各一性之意也。下大文注。统体一太极。语大莫能载。是应二五一太极言也。各具一太极。语小莫能破。是应五行各一性言也。上大文注结语所谓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夫岂有所亏欠间隔云云。所以先言此段之意。而与剥图解所言五殊二实无馀欠。精粗本末无彼此云云。皆所以明理气浑然一体之意也。如是看见。未知如何。非敢自信。不明不措。诚为请益之要。故更此烦禀。伏乞怜其愚昧。明赐批教。上李高城丈(栻)
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即本然之性。专指理言。而或者有云此性字兼气言。夫性者。人物禀受之名。故才言性字。已堕在气质中。然这个性字。是就气质中。单提性之本体而言者也。若如或者之说。则是看做气质之性。恐不然。且章句人物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云者。犹言人物皆得此理。以为五常之性也。各字所当活看。或者错认了。以为既有此各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7H 页
 得二字。是人物所禀之理。各有偏全。人虽全禀五常。物安能全禀得也云云。大槩物之本性则同。伊气质有异。故自其禀赋后观。则理绝不同。而就其禀赋初言。则性无不同。岂可谓人物所禀之理。各有偏全之殊哉。此说亦未当。未知盛意以为如何。
得二字。是人物所禀之理。各有偏全。人虽全禀五常。物安能全禀得也云云。大槩物之本性则同。伊气质有异。故自其禀赋后观。则理绝不同。而就其禀赋初言。则性无不同。岂可谓人物所禀之理。各有偏全之殊哉。此说亦未当。未知盛意以为如何。心之昏昧走作。俱是已发后病也。而或者以为昏沉时无思无虑。即未发之病也。此说如何。愚意则未发之时。莹然无私。此乃天下之大本。此时若有病可言。则中庸必不直以未发谓之中也。章句必不曰未发则性也。未知如何。
上李高城丈
昏眛之说。顷承别纸。诲谕谆勤。而愚陋之见。反复思绎。卒未领悟。气质之昏惑。一至此哉。窃念昏昧之病。虽以清粹之资。亦时有之。若以昏昧之时无思无虑观之。则似在未发境界。而非已发之病。然未发者。七情未动之前。心体虚明之时也。昏昧者。事物既接之馀。精神蒙暗之谓也。当其昏昧。未发之理则虽在其中。而不可直谓之未发之时也。故栗谷先生曰。其或昏昧或散乱者。不可谓之未发也。且昏昧与走作气象似不同。而究其所从来。则即已发之后。与物俱往。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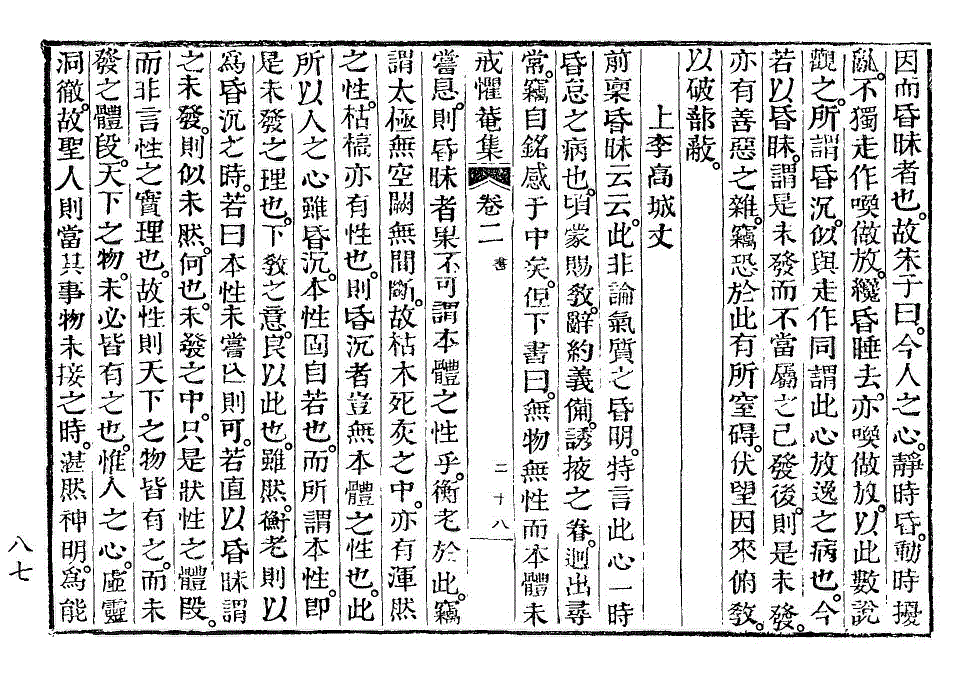 因而昏昧者也。故朱子曰。今人之心。静时昏。动时扰乱。不独走作唤做放。才昏睡去。亦唤做放。以此数说观之。所谓昏沉。似与走作同谓此心放逸之病也。今若以昏眛。谓是未发而不当属之已发后。则是未发。亦有善恶之杂。窃恐于此有所窒碍。伏望因来俯教。以破蔀蔽。
因而昏昧者也。故朱子曰。今人之心。静时昏。动时扰乱。不独走作唤做放。才昏睡去。亦唤做放。以此数说观之。所谓昏沉。似与走作同谓此心放逸之病也。今若以昏眛。谓是未发而不当属之已发后。则是未发。亦有善恶之杂。窃恐于此有所窒碍。伏望因来俯教。以破蔀蔽。上李高城丈
前禀昏昧云云。此非论气质之昏明。特言此心一时昏怠之病也。顷蒙赐教。辞约义备。诱掖之眷。迥出寻常。窃自铭感于中矣。但下书曰。无物无性而本体未尝息。则昏昧者果不可谓本体之性乎。衡老于此。窃谓太极无空阙无间断。故枯木死灰之中。亦有浑然之性。枯槁亦有性也。则昏沉者岂无本体之性也。此所以人之心虽昏沉。本性固自若也。而所谓本性。即是未发之理也。下教之意。良以此也。虽然。衡老则以为昏沉之时。若曰本性未尝亡则可。若直以昏昧谓之未发。则似未然。何也。未发之中。只是状性之体段。而非言性之实理也。故性则天下之物皆有之。而未发之体段。天下之物。未必皆有之也。惟人之心。虚灵洞彻。故圣人则当其事物未接之时。湛然神明。为能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8H 页
 全其性之德。是之谓未发。而至若众人。则只是霎时或有未发而已。走作昏昧之时盖多焉。走作昏昧之时。则性虽在中。而体段未明。不可谓之未发也。如是看见。未知如何。下教又曰。但无存存之工。则谓之大本不立。斯可矣。衡老于此。又窃谓存存者。持敬之谓。大本者。未发之谓。夫既曰昏昧者。心有偏倚。大本不立。则即此大本不立处。便可见不当谓之未发也。以此观之。则门下之意。亦似以昏昧不谓之未发。未知盛意果然否。伏乞明赐批教。
全其性之德。是之谓未发。而至若众人。则只是霎时或有未发而已。走作昏昧之时盖多焉。走作昏昧之时。则性虽在中。而体段未明。不可谓之未发也。如是看见。未知如何。下教又曰。但无存存之工。则谓之大本不立。斯可矣。衡老于此。又窃谓存存者。持敬之谓。大本者。未发之谓。夫既曰昏昧者。心有偏倚。大本不立。则即此大本不立处。便可见不当谓之未发也。以此观之。则门下之意。亦似以昏昧不谓之未发。未知盛意果然否。伏乞明赐批教。上李高城丈
下教未发之论。明白纤悉。奉读再三。窃叹理明义精之极致。但性则皆有。而未发体段。未必皆有之说。非愚妆撰得出。请毕其说焉。朱子曰。未发则性也。以此观之。未发之中。即是性也。性既无物不有。则中亦无物不有矣。然窃观张南轩以为众人无未发之时。而朱子又谓性静者须或有之。以此观之。则众人之中。惟性静者时有未发之中。而其外下愚禽兽。则不复有未发之中者明矣。愚之说。盖出于此。而初非歧看性与未发也。虽然。未发之中。即是性也。则又何故性则无物不有。而中则惟性静者有之耶。盖朱子之以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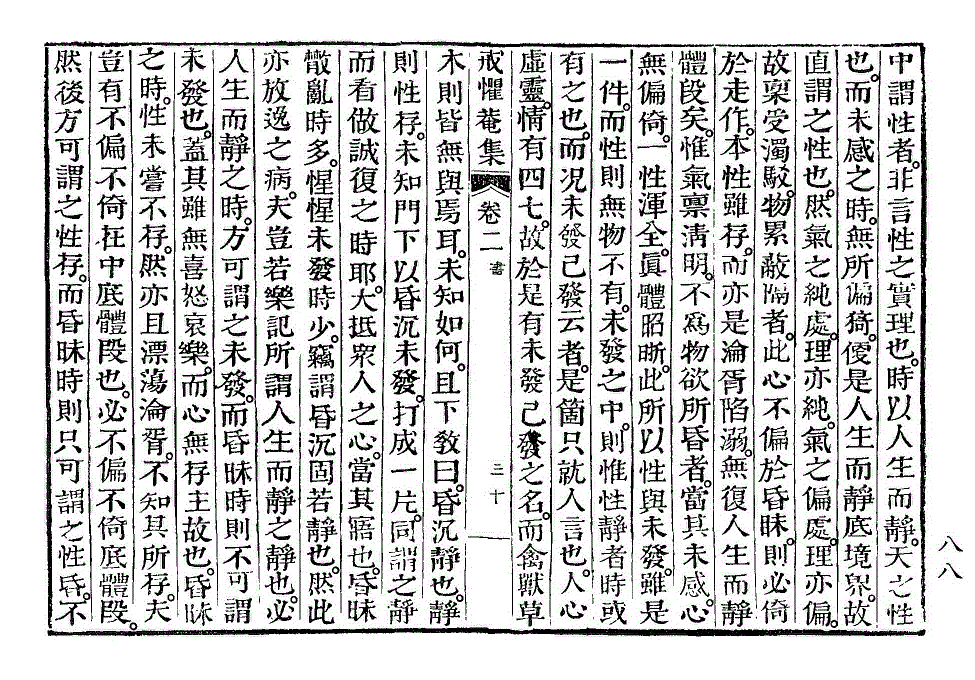 中谓性者。非言性之实理也。时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未感之时。无所偏猗。便是人生而静底境界。故直谓之性也。然气之纯处。理亦纯。气之偏处。理亦偏。故禀受浊驳。物累蔽隔者。此心不偏于昏昧。则必倚于走作。本性虽存。而亦是沦胥陷溺。无复人生而静体段矣。惟气禀清明。不为物欲所昏者。当其未感。心无偏倚。一性浑全。真体昭晢。此所以性与未发。虽是一件。而性则无物不有。未发之中。则惟性静者时或有之也。而况未发已发云者。是个只就人言也。人心虚灵。情有四七。故于是有未发已发之名。而禽兽草木则皆无与焉耳。未知如何。且下教曰。昏沉静也。静则性存。未知门下以昏沉未发。打成一片。同谓之静而看做诚复之时耶。大抵众人之心。当其寤也。昏昧散乱时多。惺惺未发时少。窃谓昏沉固若静也。然此亦放逸之病。夫岂若乐记所谓人生而静之静也。必人生而静之时。方可谓之未发。而昏昧时则不可谓未发也。盖其虽无喜怒哀乐。而心无存主故也。昏昧之时。性未尝不存。然亦且漂荡沦胥。不知其所存。夫岂有不偏不倚在中底体段也。必不偏不倚底体段。然后方可谓之性存。而昏昧时则只可谓之性昏。不
中谓性者。非言性之实理也。时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未感之时。无所偏猗。便是人生而静底境界。故直谓之性也。然气之纯处。理亦纯。气之偏处。理亦偏。故禀受浊驳。物累蔽隔者。此心不偏于昏昧。则必倚于走作。本性虽存。而亦是沦胥陷溺。无复人生而静体段矣。惟气禀清明。不为物欲所昏者。当其未感。心无偏倚。一性浑全。真体昭晢。此所以性与未发。虽是一件。而性则无物不有。未发之中。则惟性静者时或有之也。而况未发已发云者。是个只就人言也。人心虚灵。情有四七。故于是有未发已发之名。而禽兽草木则皆无与焉耳。未知如何。且下教曰。昏沉静也。静则性存。未知门下以昏沉未发。打成一片。同谓之静而看做诚复之时耶。大抵众人之心。当其寤也。昏昧散乱时多。惺惺未发时少。窃谓昏沉固若静也。然此亦放逸之病。夫岂若乐记所谓人生而静之静也。必人生而静之时。方可谓之未发。而昏昧时则不可谓未发也。盖其虽无喜怒哀乐。而心无存主故也。昏昧之时。性未尝不存。然亦且漂荡沦胥。不知其所存。夫岂有不偏不倚在中底体段也。必不偏不倚底体段。然后方可谓之性存。而昏昧时则只可谓之性昏。不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9H 页
 可谓未发之中也。未知如何。且念以昏昧谓之未发。则有甚窒碍。朱子既以未发。直谓之性。若曰昏昧是未发。则亦可以昏昧。直谓之性耶。若曰未发有善不善两样中。未发乃善底。昏昧乃不善底云。则先儒何以无如此分别说。而朱子又何以云未感时无得失可议耶。若曰昏昧虽非中而乃未发也云。则是以未发与中。歧而贰之。岂非与中庸直以未发谓中之意。尤有相悖否。愚既如此考證。又自语曰。人心有未发已发两道。既以昏昧不归之未发。则当属之已发。而昏昧静也。已发动也。又似不相涉入然。朱子曰。今人之心。静时则昏。动时扰乱。不独走作唤做放。才昏睡。亦唤做放。以此观之。则昏沉与走作。同为此心放逸之病。当属之已发后者明矣。如何。
可谓未发之中也。未知如何。且念以昏昧谓之未发。则有甚窒碍。朱子既以未发。直谓之性。若曰昏昧是未发。则亦可以昏昧。直谓之性耶。若曰未发有善不善两样中。未发乃善底。昏昧乃不善底云。则先儒何以无如此分别说。而朱子又何以云未感时无得失可议耶。若曰昏昧虽非中而乃未发也云。则是以未发与中。歧而贰之。岂非与中庸直以未发谓中之意。尤有相悖否。愚既如此考證。又自语曰。人心有未发已发两道。既以昏昧不归之未发。则当属之已发。而昏昧静也。已发动也。又似不相涉入然。朱子曰。今人之心。静时则昏。动时扰乱。不独走作唤做放。才昏睡。亦唤做放。以此观之。则昏沉与走作。同为此心放逸之病。当属之已发后者明矣。如何。上李横城丈(度远)
顷者仰问中庸率性之道与易一阴一阳之道两道字同也。下教以为一阴一阳之道。是指天地人物之理。率性之道。是经由天命之性。说得人物之理。两个道字似不同。窃思之。易所谓道字。虽统说天地万物之理。而就阴阳。指言其体。中庸所谓道字。虽只言人物。而就人物上。指言其体。两道字俱是言道之体也。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89L 页
 以此言之。恐不异矣。或有以率性之道为用。如此看则固不同。而第此道字。指体言者。断无可疑。未知崇意以为如何。
以此言之。恐不异矣。或有以率性之道为用。如此看则固不同。而第此道字。指体言者。断无可疑。未知崇意以为如何。顷禀昏沉是已发后病。承教以为昏沉即未发之病。与枯木死灰一般。老更禀未发即中也大本也。未发时宁有病。复教未发不可皆谓之中也。区区于此窃疑之。盖未发之时。莹然无私。天理浑全。不偏不倚。故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时。若有病可言。则必不直以未发谓之中也。以此观之。未发皆谓之中。有何不可耶。昏沉谓未发时病。其可乎。大抵昏沉。即此心走作。因而昏昧之谓。走作昏沉。俱是一病。故昏昧时虽若无思虑。而当此之时。直可以放逸言之。夫岂若未发之时。神守其郛而无思无虑耶。愚以昏沉为已发后病者此也。未知得否。
大学所谓明德。乃心性情之总称也。而或以为只言心。窃恐未然。以章句言之。虚灵不昧。即心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即性情也。岂可谓只言心也。未知执事于此如何看得也。愿闻之。
或者曰。气质之清浊。既得于禀赋之初。故未发之时。清浊本色自在。已发之际。善恶由此而生。衡老辨之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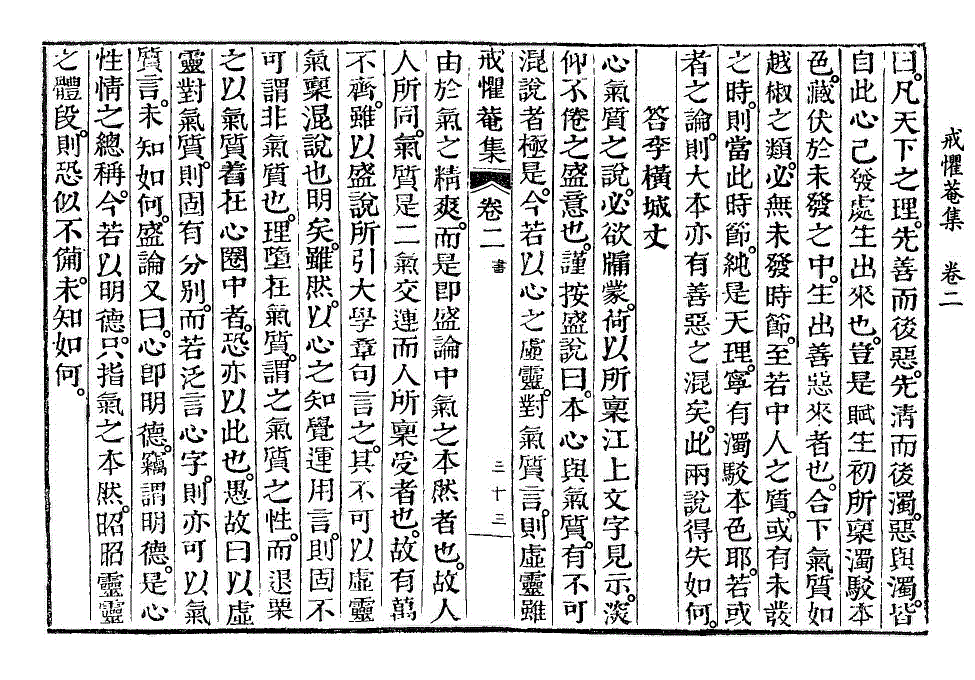 曰。凡天下之理。先善而后恶。先清而后浊。恶与浊。皆自此心已发处生出来也。岂是赋生初所禀浊驳本色。藏伏于未发之中。生出善恶来者也。合下气质如越椒之类。必无未发时节。至若中人之质。或有未发之时。则当此时节。纯是天理。宁有浊驳本色耶。若或者之论。则大本亦有善恶之混矣。此两说得失如何。
曰。凡天下之理。先善而后恶。先清而后浊。恶与浊。皆自此心已发处生出来也。岂是赋生初所禀浊驳本色。藏伏于未发之中。生出善恶来者也。合下气质如越椒之类。必无未发时节。至若中人之质。或有未发之时。则当此时节。纯是天理。宁有浊驳本色耶。若或者之论。则大本亦有善恶之混矣。此两说得失如何。答李横城丈
心气质之说。必欲牖蒙。荷以所禀江上文字见示。深仰不倦之盛意也。谨按盛说曰。本心与气质。有不可混说者极是。今若以心之虚灵。对气质言。则虚灵虽由于气之精爽。而是即盛论中气之本然者也。故人人所同。气质是二气交运而人所禀受者也。故有万不齐。虽以盛说所引大学章句言之。其不可以虚灵气禀混说也明矣。虽然。以心之知觉运用言。则固不可谓非气质也。理堕在气质。谓之气质之性。而退栗之以气质着在心圈中者。恐亦以此也。愚故曰以虚灵对气质。则固有分别。而若泛言心字。则亦可以气质言。未知如何。盛论又曰。心即明德。窃谓明德。是心性情之总称。今若以明德。只指气之本然。昭昭灵灵之体段。则恐似不备。未知如何。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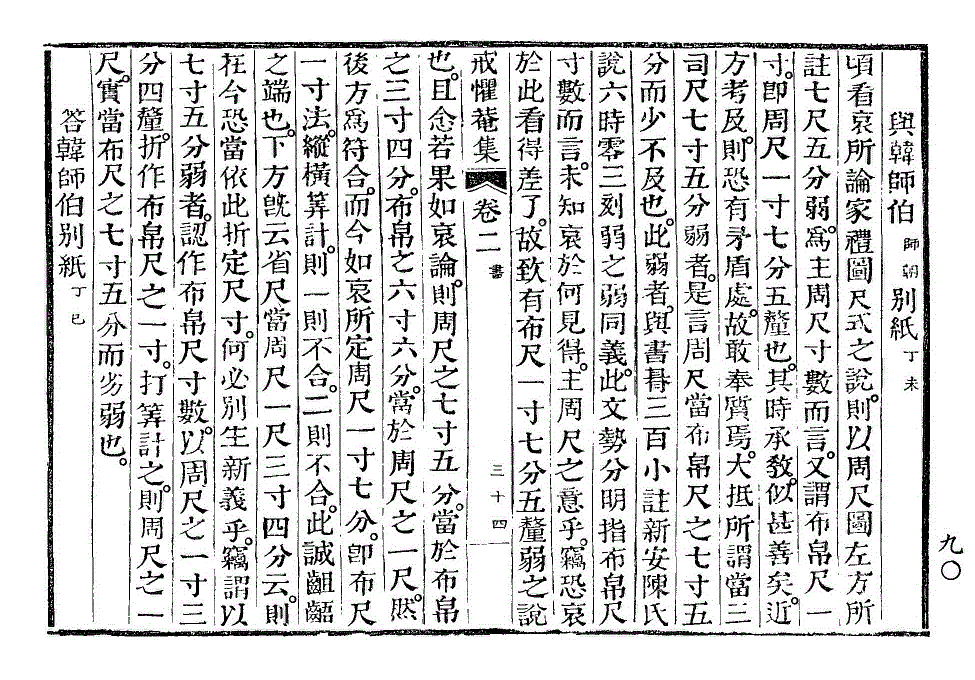 与韩师伯(师朝)别纸(丁未)
与韩师伯(师朝)别纸(丁未)顷看哀所论家礼图尺式之说。则以周尺图左方所注七尺五分弱。为主周尺寸数而言。又谓布帛尺一寸。即周尺一寸七分五釐也。其时承教。似甚善矣。近方考及。则恐有矛盾处。故敢奉质焉。大抵所谓当三司尺七寸五分弱者。是言周尺当布帛尺之七寸五分而少不及也。此弱者。与书期三百小注新安陈氏说六时零三刻弱之弱同义。此文势分明指布帛尺寸数而言。未知哀于何见得。主周尺之意乎。窃恐哀于此看得差了。故致有布尺一寸七分五釐弱之说也。且念若果如哀论。则周尺之七寸五分。当于布帛之三寸四分。布帛之六寸六分。当于周尺之一尺。然后方为符合。而今如哀所定周尺一寸七分。即布尺一寸法。纵横算计。则一则不合。二则不合。此诚龃龉之端也。下方既云省尺当周尺一尺三寸四分云。则在今恐当依此折定尺寸。何必别生新义乎。窃谓以七寸五分弱者。认作布帛尺寸数。以周尺之一寸三分四釐。折作布帛尺之一寸。打算计之。则周尺之一尺。实当布尺之七寸五分而劣弱也。
答韩师伯别纸(丁巳)
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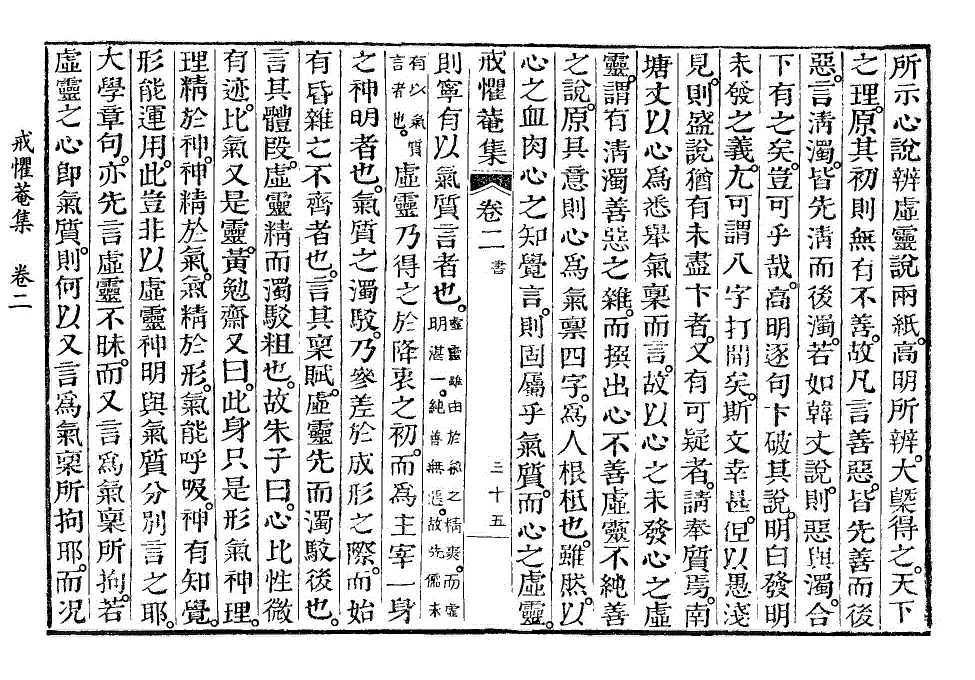 所示心说辨虚灵说两纸。高明所辨。大槩得之。天下之理。原其初则无有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清浊。皆先清而后浊。若如韩丈说。则恶与浊。合下有之矣。岂可乎哉。高明逐句卞破其说。明白发明未发之义。尤可谓八字打开矣。斯文幸甚。但以愚浅见。则盛说犹有未尽卞者。又有可疑者。请奉质焉。南塘丈以心为悉举气禀而言。故以心之未发心之虚灵。谓有清浊善恶之杂。而撰出心不善虚灵不纯善之说。原其意则心为气禀四字。为人根柢也。虽然。以心之血肉心之知觉言。则固属乎气质。而心之虚灵。则宁有以气质言者也。(虚灵虽由于气之精爽。而虚明湛一。纯善无恶。故先儒未有以气质言者也。)虚灵乃得之于降衷之初。而为主宰一身之神明者也。气质之浊驳。乃参差于成形之际。而始有昏杂之不齐者也。言其禀赋。虚灵先而浊驳后也。言其体段。虚灵精而浊驳粗也。故朱子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气又是灵。黄勉斋又曰。此身只是形气神理。理精于神。神精于气。气精于形。气能呼吸。神有知觉。形能运用。此岂非以虚灵神明与气质分别言之耶。大学章句。亦先言虚灵不昧。而又言为气禀所拘。若虚灵之心即气质。则何以又言为气禀所拘耶。而况
所示心说辨虚灵说两纸。高明所辨。大槩得之。天下之理。原其初则无有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清浊。皆先清而后浊。若如韩丈说。则恶与浊。合下有之矣。岂可乎哉。高明逐句卞破其说。明白发明未发之义。尤可谓八字打开矣。斯文幸甚。但以愚浅见。则盛说犹有未尽卞者。又有可疑者。请奉质焉。南塘丈以心为悉举气禀而言。故以心之未发心之虚灵。谓有清浊善恶之杂。而撰出心不善虚灵不纯善之说。原其意则心为气禀四字。为人根柢也。虽然。以心之血肉心之知觉言。则固属乎气质。而心之虚灵。则宁有以气质言者也。(虚灵虽由于气之精爽。而虚明湛一。纯善无恶。故先儒未有以气质言者也。)虚灵乃得之于降衷之初。而为主宰一身之神明者也。气质之浊驳。乃参差于成形之际。而始有昏杂之不齐者也。言其禀赋。虚灵先而浊驳后也。言其体段。虚灵精而浊驳粗也。故朱子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气又是灵。黄勉斋又曰。此身只是形气神理。理精于神。神精于气。气精于形。气能呼吸。神有知觉。形能运用。此岂非以虚灵神明与气质分别言之耶。大学章句。亦先言虚灵不昧。而又言为气禀所拘。若虚灵之心即气质。则何以又言为气禀所拘耶。而况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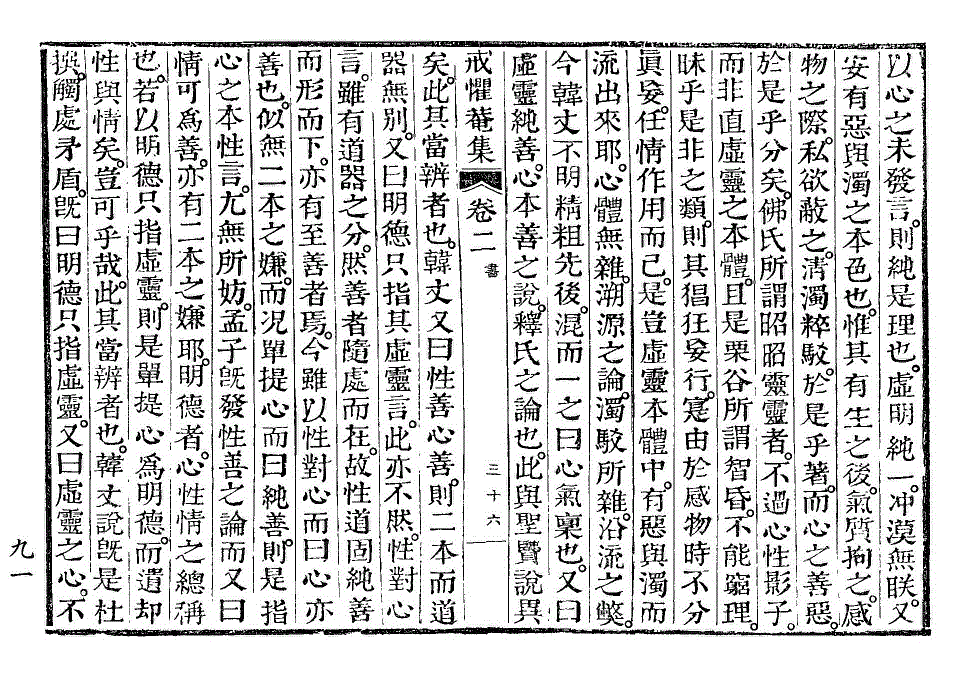 以心之未发言。则纯是理也。虚明纯一。冲漠无眹。又安有恶与浊之本色也。惟其有生之后。气质拘之。感物之际。私欲蔽之。清浊粹驳。于是乎著。而心之善恶。于是乎分矣。佛氏所谓昭昭灵灵者。不过心性影子。而非直虚灵之本体。且是栗谷所谓智昏。不能穷理。昧乎是非之类。则其猖狂妄行。寔由于感物时不分真妄。任情作用而已。是岂虚灵本体中。有恶与浊而流出来耶。心体无杂。溯源之论。浊驳所杂。沿流之弊。今韩丈不明精粗先后。混而一之曰心气禀也。又曰虚灵纯善。心本善之说。释氏之论也。此与圣贤说异矣。此其当辨者也。韩丈又曰性善心善。则二本而道器无别。又曰明德只指其虚灵言。此亦不然。性对心言。虽有道器之分。然善者随处而在。故性道固纯善而形而下。亦有至善者焉。今虽以性对心而曰心亦善也。似无二本之嫌。而况单提心而曰纯善。则是指心之本性言。尤无所妨。孟子既发性善之论而又曰情可为善。亦有二本之嫌耶。明德者。心性情之总称也。若以明德只指虚灵。则是单提心为明德。而遗却性与情矣。岂可乎哉。此其当辨者也。韩丈说既是杜撰。触处矛盾。既曰明德只指虚灵。又曰虚灵之心。不
以心之未发言。则纯是理也。虚明纯一。冲漠无眹。又安有恶与浊之本色也。惟其有生之后。气质拘之。感物之际。私欲蔽之。清浊粹驳。于是乎著。而心之善恶。于是乎分矣。佛氏所谓昭昭灵灵者。不过心性影子。而非直虚灵之本体。且是栗谷所谓智昏。不能穷理。昧乎是非之类。则其猖狂妄行。寔由于感物时不分真妄。任情作用而已。是岂虚灵本体中。有恶与浊而流出来耶。心体无杂。溯源之论。浊驳所杂。沿流之弊。今韩丈不明精粗先后。混而一之曰心气禀也。又曰虚灵纯善。心本善之说。释氏之论也。此与圣贤说异矣。此其当辨者也。韩丈又曰性善心善。则二本而道器无别。又曰明德只指其虚灵言。此亦不然。性对心言。虽有道器之分。然善者随处而在。故性道固纯善而形而下。亦有至善者焉。今虽以性对心而曰心亦善也。似无二本之嫌。而况单提心而曰纯善。则是指心之本性言。尤无所妨。孟子既发性善之论而又曰情可为善。亦有二本之嫌耶。明德者。心性情之总称也。若以明德只指虚灵。则是单提心为明德。而遗却性与情矣。岂可乎哉。此其当辨者也。韩丈说既是杜撰。触处矛盾。既曰明德只指虚灵。又曰虚灵之心。不戒惧庵集卷之二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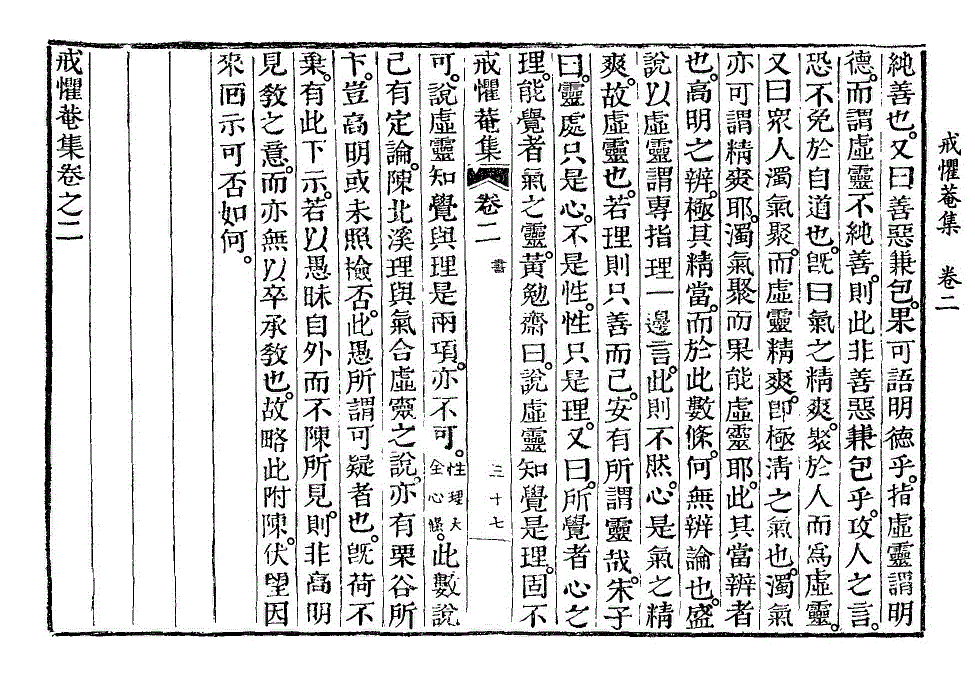 纯善也。又曰善恶兼包。果可语明德乎。指虚灵谓明德。而谓虚灵不纯善。则此非善恶兼包乎。攻人之言。恐不免于自道也。既曰气之精爽。聚于人而为虚灵。又曰众人浊气聚。而虚灵精爽。即极清之气也。浊气亦可谓精爽耶。浊气聚而果能虚灵耶。此其当辨者也。高明之辨。极其精当。而于此数条。何无辨论也。盛说以虚灵谓专指理一边言。此则不然。心是气之精爽。故虚灵也。若理则只善而已。安有所谓灵哉。朱子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黄勉斋曰。说虚灵知觉是理。固不可。说虚灵知觉与理是两项。亦不可。(性理大全心条。)此数说已有定论。陈北溪理与气合虚灵之说。亦有栗谷所卞。岂高明或未照检否。此愚所谓可疑者也。既荷不弃。有此下示。若以愚昧自外而不陈所见。则非高明见教之意。而亦无以卒承教也。故略此附陈。伏望因来回示可否如何。
纯善也。又曰善恶兼包。果可语明德乎。指虚灵谓明德。而谓虚灵不纯善。则此非善恶兼包乎。攻人之言。恐不免于自道也。既曰气之精爽。聚于人而为虚灵。又曰众人浊气聚。而虚灵精爽。即极清之气也。浊气亦可谓精爽耶。浊气聚而果能虚灵耶。此其当辨者也。高明之辨。极其精当。而于此数条。何无辨论也。盛说以虚灵谓专指理一边言。此则不然。心是气之精爽。故虚灵也。若理则只善而已。安有所谓灵哉。朱子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黄勉斋曰。说虚灵知觉是理。固不可。说虚灵知觉与理是两项。亦不可。(性理大全心条。)此数说已有定论。陈北溪理与气合虚灵之说。亦有栗谷所卞。岂高明或未照检否。此愚所谓可疑者也。既荷不弃。有此下示。若以愚昧自外而不陈所见。则非高明见教之意。而亦无以卒承教也。故略此附陈。伏望因来回示可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