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x 页
䨓渊集卷之十四
记
记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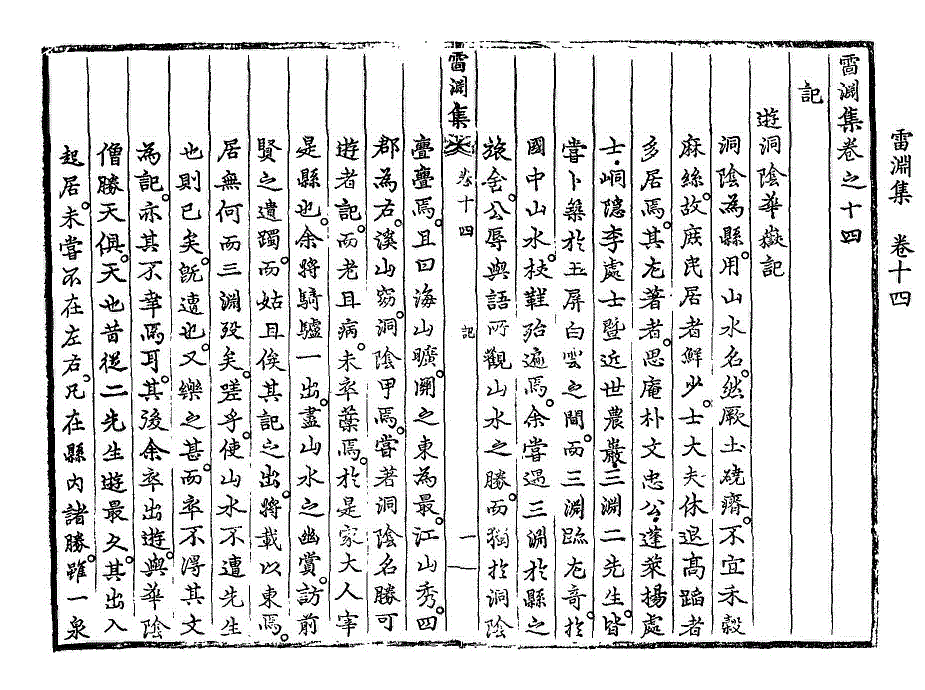 游洞阴华岳记
游洞阴华岳记洞阴为县。用山水名。然厥土硗瘠。不宜禾谷麻丝。故庶民居者鲜少。士大夫休退高蹈者多居焉。其尤著者。思庵朴文忠公,蓬莱杨处士,峒隐李处士暨近世农岩,三渊二先生。皆尝卜筑于玉屏白云之间。而三渊迹尤奇。于国中山水。杖鞋殆遍焉。余尝遇三渊于县之旅舍。公辱与语所观山水之胜。而独于洞阴亹亹焉。且曰海山旷。关之东为最。江山秀。四郡为右。溪山窈。洞阴甲焉。尝著洞阴名胜可游者记。而老且病。未卒藁焉。于是家大人宰是县也。余将骑驴一出。尽山水之幽赏。访前贤之遗躅。而姑且俟其记之出。将载以东焉。居无何而三渊殁矣。嗟乎。使山水不遭先生也则已矣。既遭也。又乐之甚。而卒不得其文为记。亦其不幸焉耳。其后余卒出游。与华阴僧胜天俱。天也昔从二先生游最久。其出入起居。未尝不在左右。凡在县内诸胜。虽一泉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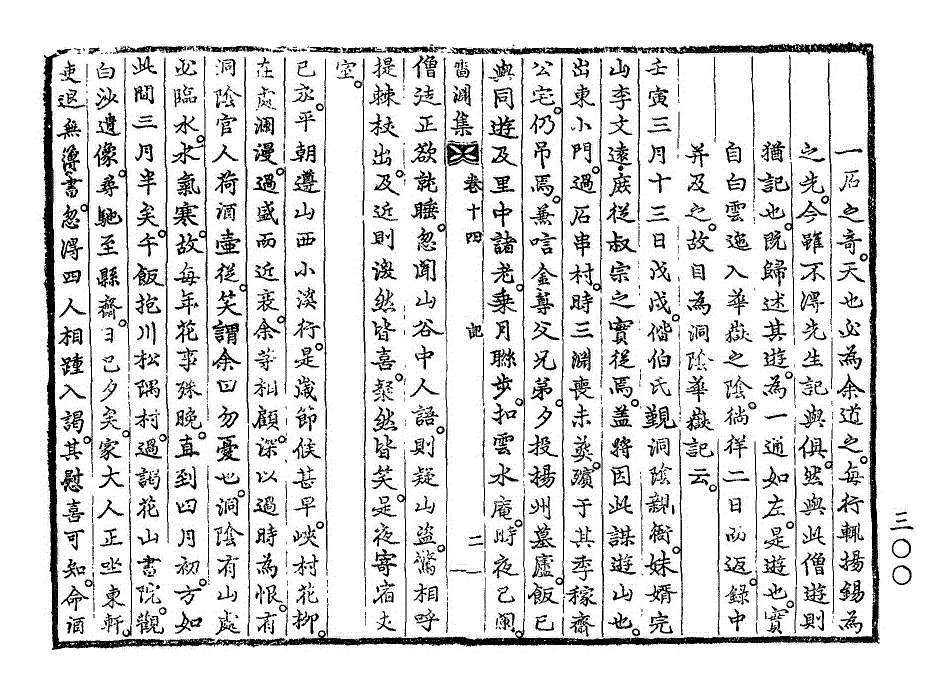 一石之奇。天也必为余道之。每行辄扬锡为之先。今虽不得先生记与俱。然与此僧游则犹记也。既归述其游。为一通如左。是游也。实自白云迤入华岳之阴。徜徉二日而返。录中并及之。故目为洞阴华岳记云。
一石之奇。天也必为余道之。每行辄扬锡为之先。今虽不得先生记与俱。然与此僧游则犹记也。既归述其游。为一通如左。是游也。实自白云迤入华岳之阴。徜徉二日而返。录中并及之。故目为洞阴华岳记云。壬寅三月十三日戊戌。偕伯氏觐洞阴亲衙。妹婿完山李文远,庶从叔宗之实从焉。盖将因此谋游山也。出东小门。过石串村。时三渊丧未葬。殡于其季稼斋公宅。仍吊焉。兼唁金尊父兄弟。夕投杨州墓庐。饭已与同游及里中诸老。乘月联步。扣云水庵。时夜已阑。僧徒正欲就睡。忽闻山谷中人语。则疑山盗。惊相呼提棘杖出。及近则涣然皆喜。粲然皆笑。是夜寄宿丈室。
己亥。平朝遵山西小溪行。是岁节候甚早。峡村花柳。在处澜漫。过盛而近衰。余等相顾。深以过时为恨。有洞阴官人荷酒壶从。笑谓余曰勿忧也。洞阴有山处必临水。水气寒。故每年花事殊晚。直到四月初。方如此间三月半矣。午饭抱川松隅村。过谒花山书院。观白沙遗像。寻驰至县斋。日已夕矣。家大人正坐东轩。吏退无簿书。忽得四人相踵入谒。其慰喜可知。命酒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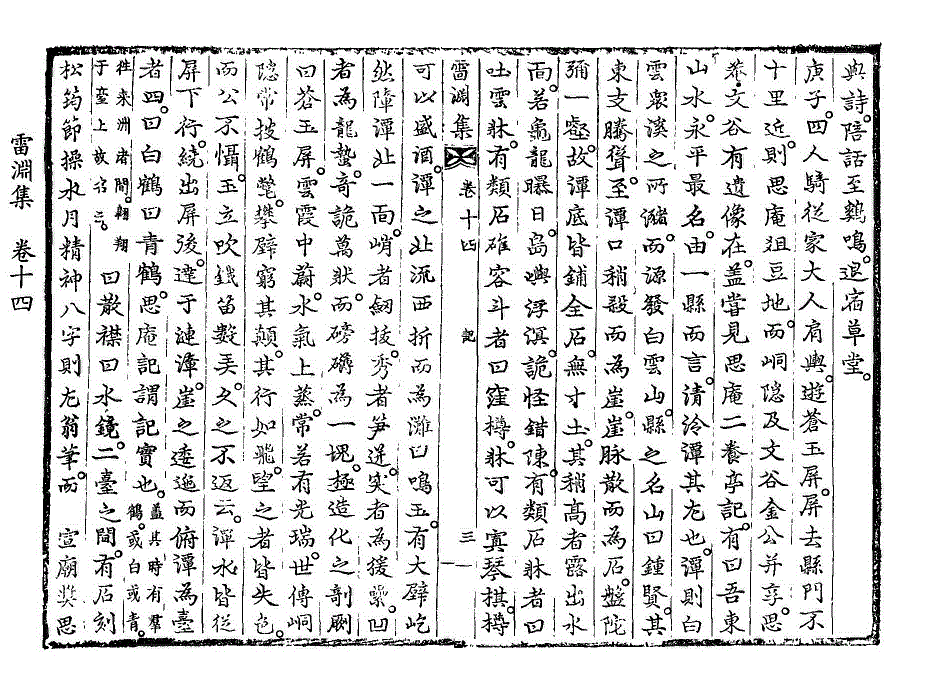 与诗。陪话至鸡鸣。退宿草堂。
与诗。陪话至鸡鸣。退宿草堂。庚子。四人骑从家大人肩舆。游苍玉屏。屏去县门不十里近。则思庵俎豆地。而峒隐及文谷金公并享。思庵,文谷有遗像在。盖尝见思庵二养亭记。有曰吾东山水。永平最名。由一县而言。清泠潭其尤也。潭则白云众溪之所潴。而源发白云山。县之名山曰钟贤。其东支腾耸。至潭口稍杀而为崖。崖脉散而为石。盘陀弥一壑。故潭底皆铺全石。无寸土。其稍高者露出水面。若龟龙曝日。岛屿浮溟。诡怪错陈。有类石床者曰吐云床。有类石碓容斗者曰洼樽。床可以寘琴棋。樽可以盛酒。潭之北流西折而为滩曰鸣玉。有大壁屹然障潭北一面。峭者剑拔。秀者笋迸。突者为猿累。凹者为龙蛰。奇诡万状。而磅礴为一块。极造化之剞劂曰苍玉屏。云霞中蔚。水气上蒸。常若有光瑞。世传峒隐常披鹤氅。攀壁穷其颠。其行如飞。望之者皆失色。而公不慑。玉立吹铁笛数弄。久之不返云。潭水皆从屏下行。绕出屏后。达于涟漳。崖之逶迤而俯潭为台者四。曰白鹤曰青鹤。思庵记谓记实也。(盖其时有群鹤。或白或青。往来洲渚间。翱翔于台上故名云。)曰散襟曰水镜。二台之间。有石刻松筠节操水月精神八字则尤翁笔。而 宣庙奖思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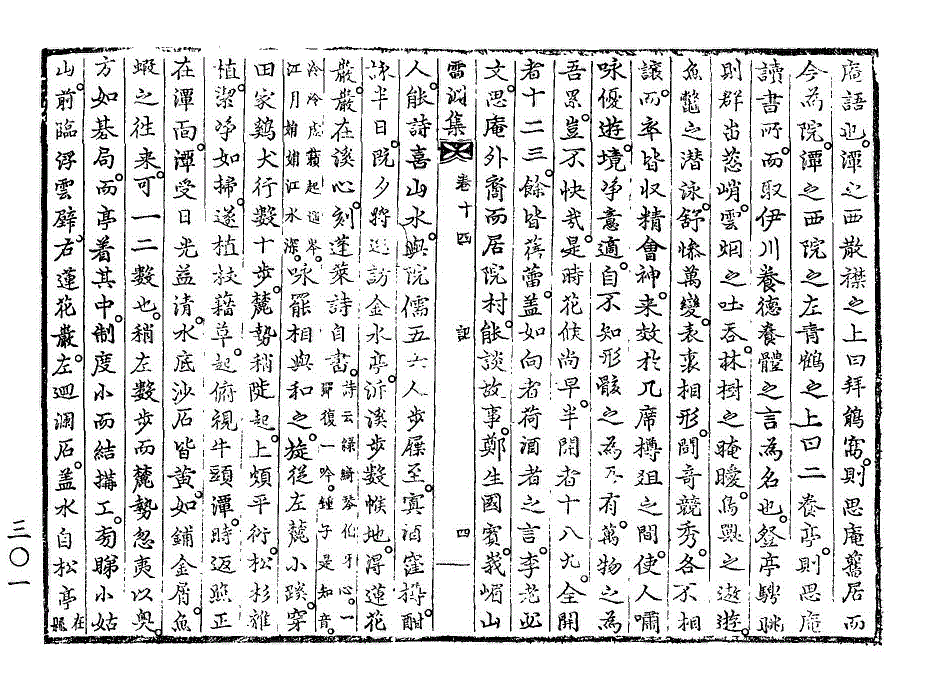 庵语也。潭之西散襟之上曰拜鹃窝。则思庵旧居而今为院。潭之西院之左青鹤之上曰二养亭。则思庵读书所。而取伊川养德养体之言为名也。登亭骋眺则群岫葱峭。云烟之吐吞。林树之晻暧。鸟兽之遨游。鱼鳖之潜泳。舒惨万变。表里相形。斗奇竞秀。各不相让。而卒皆收精会神。来效于几席樽俎之间。使人啸咏优游。境净意适。自不知形骸之为吾有。万物之为吾累。岂不快哉。是时花候尚早。半开者十八九。全开者十二三。馀皆蓓蕾。盖如向者荷酒者之言。李老必文。思庵外裔而居院村。能谈故事。郑生国宾。峨嵋山人。能诗喜山水。与院儒五六人步屧至。寘酒洼樽。酣咏半日。既夕将迤访金水亭。溯溪步数帿地。得莲花岩。岩在溪心。刻蓬莱诗自书。(诗云绿绮琴伯牙心。一弹复一吟。钟子是知音。泠泠虚籁起遥岑。江月娟娟江水深。)咏罢相与和之。旋从左麓小蹊。穿田家鸡犬行数十步。麓势稍陡起。上颇平衍。松杉杂植。洁净如扫。遂植杖藉草。起俯视牛头潭。时返照正在潭面。潭受日光益清。水底沙石皆黄。如铺金屑。鱼虾之往来。可一二数也。稍左数步而麓势忽夷以奥。方如棋局。而亭着其中。制度小而结搆工。旁睇小姑山。前临浮云壁。右莲花岩。左回澜石。盖水自松亭(在县
庵语也。潭之西散襟之上曰拜鹃窝。则思庵旧居而今为院。潭之西院之左青鹤之上曰二养亭。则思庵读书所。而取伊川养德养体之言为名也。登亭骋眺则群岫葱峭。云烟之吐吞。林树之晻暧。鸟兽之遨游。鱼鳖之潜泳。舒惨万变。表里相形。斗奇竞秀。各不相让。而卒皆收精会神。来效于几席樽俎之间。使人啸咏优游。境净意适。自不知形骸之为吾有。万物之为吾累。岂不快哉。是时花候尚早。半开者十八九。全开者十二三。馀皆蓓蕾。盖如向者荷酒者之言。李老必文。思庵外裔而居院村。能谈故事。郑生国宾。峨嵋山人。能诗喜山水。与院儒五六人步屧至。寘酒洼樽。酣咏半日。既夕将迤访金水亭。溯溪步数帿地。得莲花岩。岩在溪心。刻蓬莱诗自书。(诗云绿绮琴伯牙心。一弹复一吟。钟子是知音。泠泠虚籁起遥岑。江月娟娟江水深。)咏罢相与和之。旋从左麓小蹊。穿田家鸡犬行数十步。麓势稍陡起。上颇平衍。松杉杂植。洁净如扫。遂植杖藉草。起俯视牛头潭。时返照正在潭面。潭受日光益清。水底沙石皆黄。如铺金屑。鱼虾之往来。可一二数也。稍左数步而麓势忽夷以奥。方如棋局。而亭着其中。制度小而结搆工。旁睇小姑山。前临浮云壁。右莲花岩。左回澜石。盖水自松亭(在县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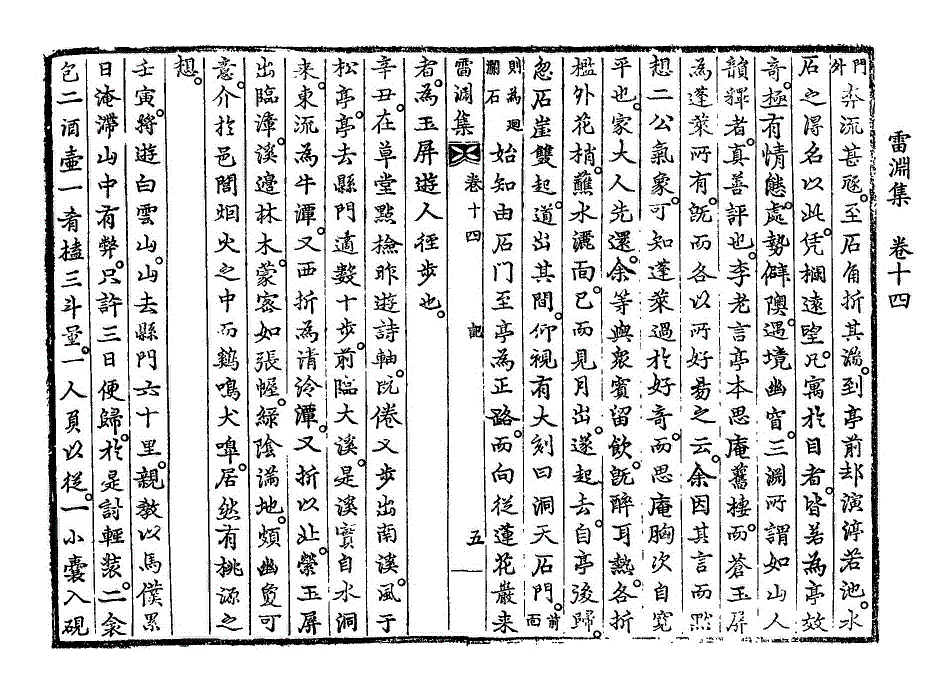 门外)奔流甚豗。至石角折其湍。到亭前却演渟若池。水石之得名以此。凭栏远望。凡寓于目者。皆若为亭效奇。极有情态。处势僻隩。遇境幽窅。三渊所谓如山人韵释者。真善评也。李老言亭本思庵旧栖。而苍玉屏为蓬莱所有。既而各以所好易之云。余因其言而默想二公气象。可知蓬莱过于好奇。而思庵胸次自宽平也。家大人先还。余等与众宾留饮。既醉耳热。各折槛外花梢。蘸水洒面。已而见月出。遂起去。自亭后归。忽石崖双起。道出其间。仰视有大刻曰洞天石门。(前面则为回澜石)始知由石门至亭为正路。而向从莲花岩来者。为玉屏游人径步也。
门外)奔流甚豗。至石角折其湍。到亭前却演渟若池。水石之得名以此。凭栏远望。凡寓于目者。皆若为亭效奇。极有情态。处势僻隩。遇境幽窅。三渊所谓如山人韵释者。真善评也。李老言亭本思庵旧栖。而苍玉屏为蓬莱所有。既而各以所好易之云。余因其言而默想二公气象。可知蓬莱过于好奇。而思庵胸次自宽平也。家大人先还。余等与众宾留饮。既醉耳热。各折槛外花梢。蘸水洒面。已而见月出。遂起去。自亭后归。忽石崖双起。道出其间。仰视有大刻曰洞天石门。(前面则为回澜石)始知由石门至亭为正路。而向从莲花岩来者。为玉屏游人径步也。辛丑。在草堂点检昨游诗轴。既倦又步出南溪。风于松亭。亭去县门适数十步。前临大溪。是溪实自水洞来。东流为牛潭。又西折为清泠潭。又折以北。萦玉屏出临漳。溪边林木。蒙密如张幄。绿阴满地。颇幽夐可意。介于邑闾烟火之中而鸡鸣犬嗥。居然有桃源之想。
壬寅。将游白云山。山去县门六十里。亲教以马仆累日淹滞山中有弊。只许三日便归。于是讨轻装。二衾包二酒壶一肴榼三斗量。一人负以从。一小囊入砚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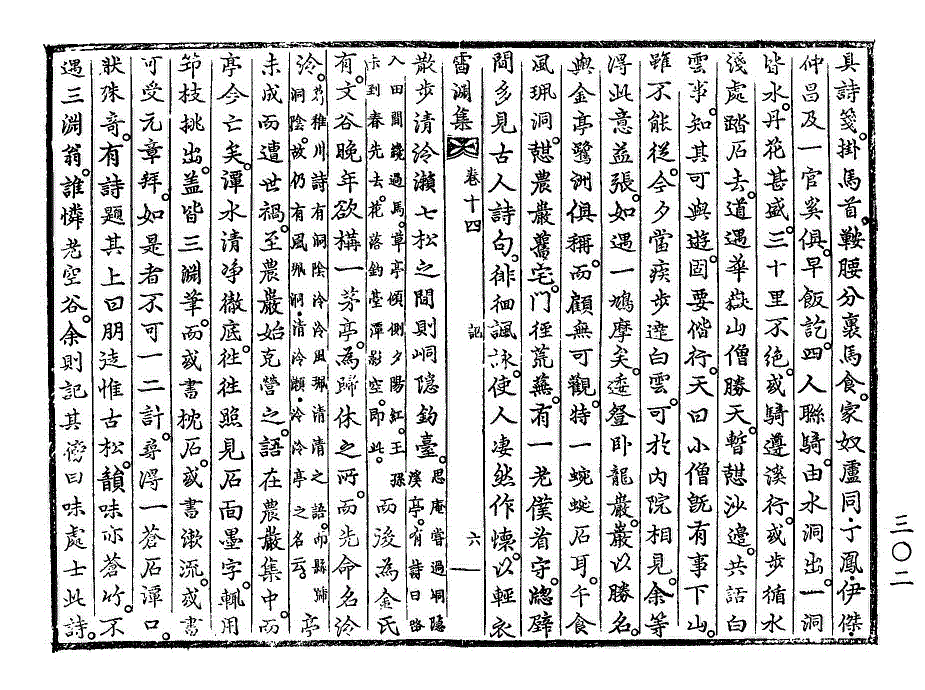 具诗笺。挂马首。鞍腰分裹马食。家奴卢同,丁凤,伊杰,仲昌及一官奚俱。早饭讫。四人联骑。由水洞出。一洞皆水。丹花甚盛。三十里不绝。或骑遵溪行。或步循水浅处踏石去。道遇华岳山僧胜天。暂憩沙边。共话白云事。知其可与游。固要偕行。天曰小僧既有事下山。虽不能从。今夕当疾步达白云。可于内院相见。余等得此意益张。如遇一鸠摩矣。逶登卧龙岩。岩以胜名。与金亭鹭洲俱称。而顾无可观。特一蜿蜒石耳。午食风佩洞。憩农岩旧宅。门径荒芜。有一老仆看守。窗壁间多见古人诗句。徘徊讽咏。使人凄然作怀。以轻衣散步清泠濑七松之间则峒隐钓台。(思庵尝过峒隐溪亭。有诗曰路入田间才过马。草亭倾侧夕阳红。王孙未到春先去。花落钓台潭影空。即此。)而后为金氏有。文谷晚年欲构一茅亭。为归休之所。而先命名泠泠。(葛稚川诗有洞阴泠泠风佩清清之语。而县号洞阴。故仍有风佩洞,清泠濑,泠泠亭之名云。)亭未成而遭世祸。至农岩始克营之。语在农岩集中。而亭今亡矣。潭水清净彻底。往往照见石面墨字。辄用筇枝挑出。盖皆三渊笔。而或书枕石。或书漱流。或书可受元章拜。如是者不可一二计。寻得一苍石潭口。状殊奇。有诗题其上曰朋徒惟古松。韵味亦苍竹。不遇三渊翁。谁怜老空谷。余则记其傍曰味处士此诗。
具诗笺。挂马首。鞍腰分裹马食。家奴卢同,丁凤,伊杰,仲昌及一官奚俱。早饭讫。四人联骑。由水洞出。一洞皆水。丹花甚盛。三十里不绝。或骑遵溪行。或步循水浅处踏石去。道遇华岳山僧胜天。暂憩沙边。共话白云事。知其可与游。固要偕行。天曰小僧既有事下山。虽不能从。今夕当疾步达白云。可于内院相见。余等得此意益张。如遇一鸠摩矣。逶登卧龙岩。岩以胜名。与金亭鹭洲俱称。而顾无可观。特一蜿蜒石耳。午食风佩洞。憩农岩旧宅。门径荒芜。有一老仆看守。窗壁间多见古人诗句。徘徊讽咏。使人凄然作怀。以轻衣散步清泠濑七松之间则峒隐钓台。(思庵尝过峒隐溪亭。有诗曰路入田间才过马。草亭倾侧夕阳红。王孙未到春先去。花落钓台潭影空。即此。)而后为金氏有。文谷晚年欲构一茅亭。为归休之所。而先命名泠泠。(葛稚川诗有洞阴泠泠风佩清清之语。而县号洞阴。故仍有风佩洞,清泠濑,泠泠亭之名云。)亭未成而遭世祸。至农岩始克营之。语在农岩集中。而亭今亡矣。潭水清净彻底。往往照见石面墨字。辄用筇枝挑出。盖皆三渊笔。而或书枕石。或书漱流。或书可受元章拜。如是者不可一二计。寻得一苍石潭口。状殊奇。有诗题其上曰朋徒惟古松。韵味亦苍竹。不遇三渊翁。谁怜老空谷。余则记其傍曰味处士此诗。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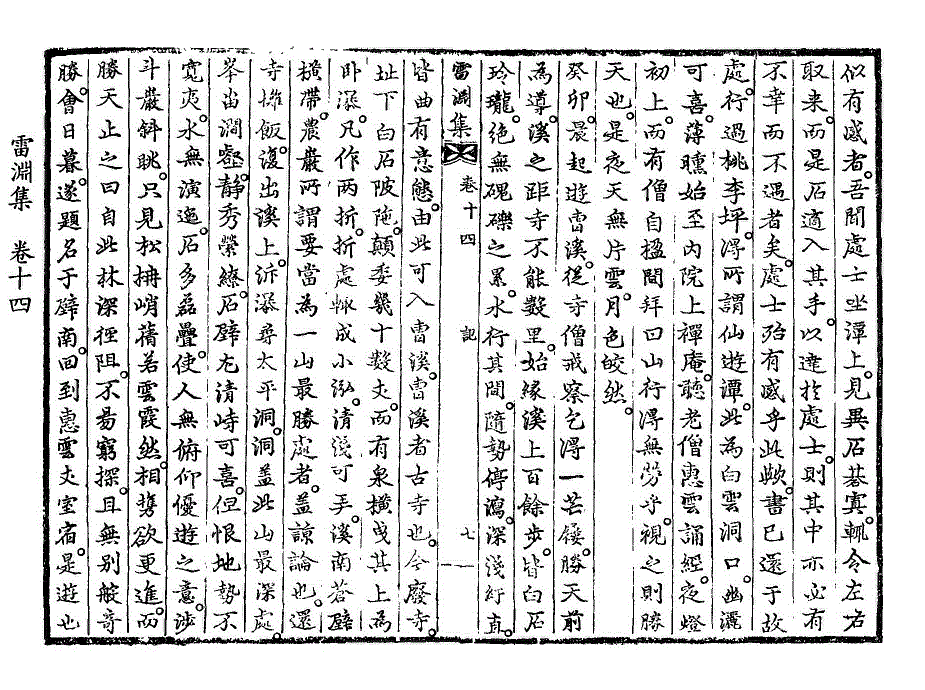 似有感者。吾闻处士坐潭上。见异石棋寘。辄令左右取来。而是石适入其手。以达于处士。则其中亦必有不幸而不遇者矣。处士殆有感乎此欤。书已还于故处。行过桃李坪。得所谓仙游潭。此为白云洞口。幽洒可喜。薄曛始至内院上禅庵。听老僧惠云诵经。夜灯初上。而有僧自楹间拜曰山行得无劳乎。视之则胜天也。是夜天无片云。月色皎然。
似有感者。吾闻处士坐潭上。见异石棋寘。辄令左右取来。而是石适入其手。以达于处士。则其中亦必有不幸而不遇者矣。处士殆有感乎此欤。书已还于故处。行过桃李坪。得所谓仙游潭。此为白云洞口。幽洒可喜。薄曛始至内院上禅庵。听老僧惠云诵经。夜灯初上。而有僧自楹间拜曰山行得无劳乎。视之则胜天也。是夜天无片云。月色皎然。癸卯。晨起游曹溪。从寺僧戒察乞得一芒屦。胜天前为导。溪之距寺不能数里。始缘溪上百馀步。皆白石玲珑。绝无磈砾之累。水行其间。随势停泻。深浅纡直。皆曲有意态。由此可入曹溪。曹溪者古寺也。今废寺。址下白石陂陁。颠委几十数丈。而有泉横曳其上为卧瀑。凡作两折。折处辄成小泓。清浅可弄。溪南苍壁横带。农岩所谓要当为一山最胜处者。盖谅论也。还寺摊饭。复出溪上。溯瀑寻太平洞。洞盖此山最深处。峰岫涧壑。静秀萦缭。石壁尤清峙可喜。但恨地势不宽夷。水无演迤。石多磊叠。使人无俯仰优游之意。涉斗岩斜眺。只见松楠峭茜若云霞然。相携欲更进。而胜天止之曰自此林深径阻。不易穷探。且无别般奇胜。会日暮。遂题名于壁南。回到惠云丈室宿。是游也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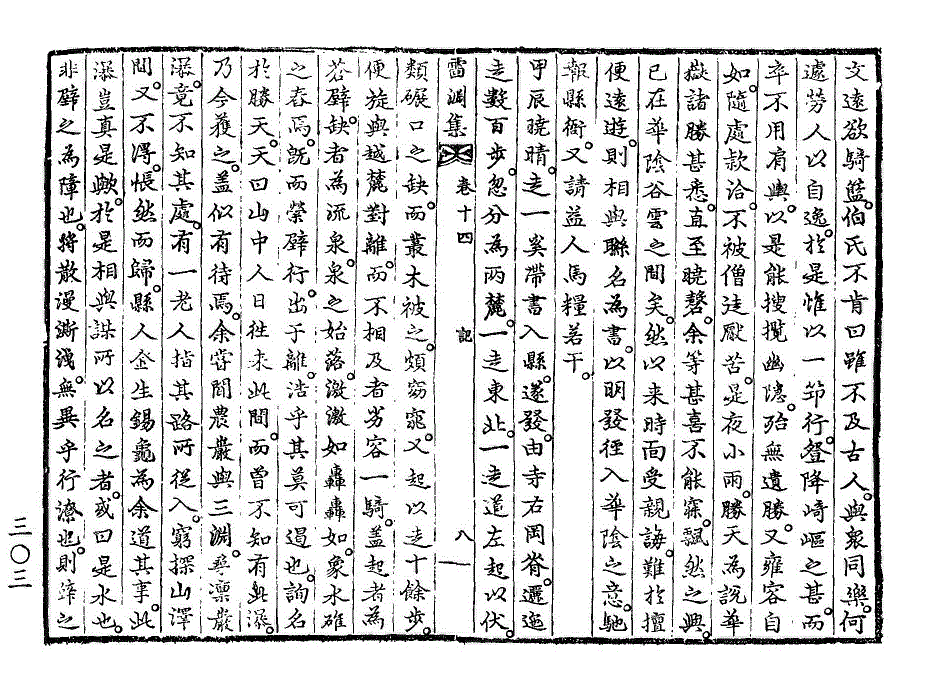 文远欲骑篮。伯氏不肯曰虽不及古人。与众同乐。何遽劳人以自逸。于是惟以一筇行。登降崎岖之甚。而卒不用肩舆。以是能搜揽幽隐。殆无遗胜。又雍容自如。随处款洽。不被僧徒厌苦。是夜小雨。胜天为说华岳诸胜甚悉。直至晓磬。余等甚喜不能寐。飘然之兴。已在华阴谷云之间矣。然以来时面受亲诲。难于擅便远游。则相与联名为书。以明发径入华阴之意。驰报县衙。又请益人马粮若干。
文远欲骑篮。伯氏不肯曰虽不及古人。与众同乐。何遽劳人以自逸。于是惟以一筇行。登降崎岖之甚。而卒不用肩舆。以是能搜揽幽隐。殆无遗胜。又雍容自如。随处款洽。不被僧徒厌苦。是夜小雨。胜天为说华岳诸胜甚悉。直至晓磬。余等甚喜不能寐。飘然之兴。已在华阴谷云之间矣。然以来时面受亲诲。难于擅便远游。则相与联名为书。以明发径入华阴之意。驰报县衙。又请益人马粮若干。甲辰晓晴。走一奚带书入县。遂发。由寺右冈脊。逦迤走数百步。忽分为两麓。一走东北。一走道左起以伏。类碾口之缺。而丛木被之。颇窈窕。又起以走十馀步。便旋与越麓对离。而不相及者劣容一骑。盖起者为苍壁。缺者为流泉。泉之始落。激激如轰轰如。象水碓之舂焉。既而萦壁行。出于离。浩乎其莫可遏也。询名于胜天。天曰山中人日往来此间。而曾不知有此瀑。乃今获之。盖似有待焉。余尝闻农岩与三渊。寻凛岩瀑。竟不知其处。有一老人指其路所从入。穷探山泽间。又不得。怅然而归。县人金生锡龟为余道其事。此瀑岂真是欤。于是相与谋所以名之者。或曰是水也。非壁之为障也。将散漫澌泄。无异乎行潦也。则壁之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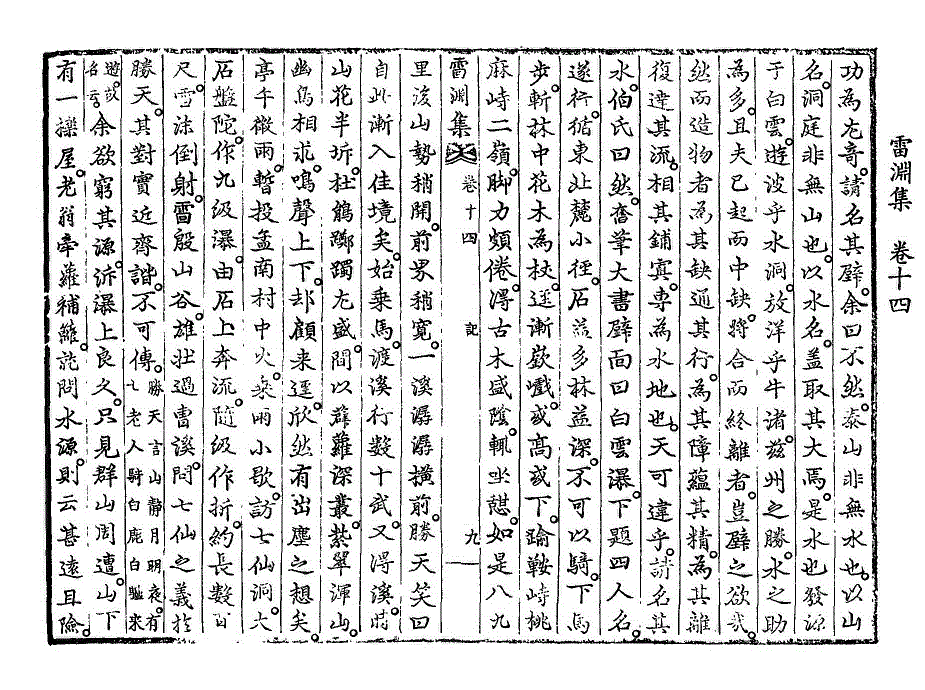 功为尤奇。请名其壁。余曰不然。泰山非无水也。以山名。洞庭非无山也。以水名。盖取其大焉。是水也发源于白云。游波乎水洞。放洋乎牛渚。玆州之胜。水之助为多。且夫已起而中缺。将合而终离者。岂壁之欲哉。然而造物者为其缺通其行。为其障蕴其精。为其离复达其流。相其铺寘。专为水地也。天可违乎。请名其水。伯氏曰然。奋笔大书壁面曰白云瀑。下题四人名。遂行。循东北麓小径。石益多林益深。不可以骑。下马步。斩林中花木为杖。径渐嵚巇。或高或下。踰鞍峙桃麻峙二岭。脚力颇倦。得古木盛阴。辄坐憩。如是八九里后山势稍开。前界稍宽。一溪潺潺横前。胜天笑曰自此渐入佳境矣。始乘马。渡溪行数十武。又得溪。时山花半坼。杜鹃踯躅尤盛。间以薜萝深丛。紫翠浑山。幽鸟相求。鸣声上下。却顾来径。欣然有出尘之想矣。亭午微雨。暂投孟南村中火。乘雨小歇。访七仙洞。大石盘陀。作九级瀑。由石上奔流。随级作折。约长数百尺。雪沫倒射。䨓殷山谷。雄壮过曹溪。问七仙之义于胜天。其对实近齐谐。不可传。(胜天言山静月明夜。有七老人骑白鹿白驴来游。故名云。)余欲穷其源。溯瀑上良久。只见群山周遭。山下有一栎屋。老翁牵萝补篱。就问水源。则云甚远且险。
功为尤奇。请名其壁。余曰不然。泰山非无水也。以山名。洞庭非无山也。以水名。盖取其大焉。是水也发源于白云。游波乎水洞。放洋乎牛渚。玆州之胜。水之助为多。且夫已起而中缺。将合而终离者。岂壁之欲哉。然而造物者为其缺通其行。为其障蕴其精。为其离复达其流。相其铺寘。专为水地也。天可违乎。请名其水。伯氏曰然。奋笔大书壁面曰白云瀑。下题四人名。遂行。循东北麓小径。石益多林益深。不可以骑。下马步。斩林中花木为杖。径渐嵚巇。或高或下。踰鞍峙桃麻峙二岭。脚力颇倦。得古木盛阴。辄坐憩。如是八九里后山势稍开。前界稍宽。一溪潺潺横前。胜天笑曰自此渐入佳境矣。始乘马。渡溪行数十武。又得溪。时山花半坼。杜鹃踯躅尤盛。间以薜萝深丛。紫翠浑山。幽鸟相求。鸣声上下。却顾来径。欣然有出尘之想矣。亭午微雨。暂投孟南村中火。乘雨小歇。访七仙洞。大石盘陀。作九级瀑。由石上奔流。随级作折。约长数百尺。雪沫倒射。䨓殷山谷。雄壮过曹溪。问七仙之义于胜天。其对实近齐谐。不可传。(胜天言山静月明夜。有七老人骑白鹿白驴来游。故名云。)余欲穷其源。溯瀑上良久。只见群山周遭。山下有一栎屋。老翁牵萝补篱。就问水源。则云甚远且险。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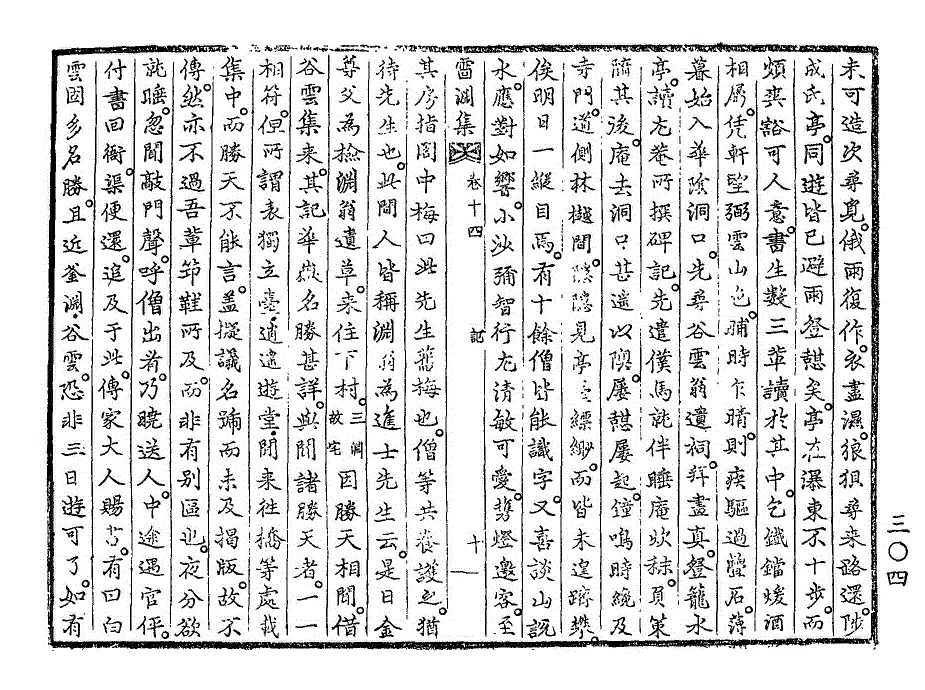 未可造次寻觅。俄雨复作。衣尽湿。狼狈寻来路还。陟成氏亭。同游皆已避雨登憩矣。亭在瀑东不十步。而颇爽豁可人意。书生数三辈读于其中。乞铁铛煖酒相属。凭轩望弼云山色。晡时乍晴。则疾驱过叠石。薄暮始入华阴洞口。先寻谷云翁遗祠。拜画真。登笼水亭。读尤庵所撰碑记。先遣仆马就伴睡庵炊秣。负策随其后。庵去洞口甚遥以隩。屡憩屡起。钟鸣时才及寺门。道侧林樾间。隐隐见亭台缥缈。而皆未遑跻攀。俟明日一纵目焉。有十馀僧皆能识字。又喜谈山说水。应对如响。小沙弥智行尤清敏可爱。携灯邀客。至其房指阁中梅曰此先生旧梅也。僧等共养护之。犹待先生也。此间人皆称渊翁为进士先生云。是日金尊父为检渊翁遗草。来住下村。(三渊故宅。)因胜天相闻。借谷云集来。其记华岳名胜甚详。与闻诸胜天者。一一相符。但所谓表独立台,逍遥游堂,閒来往桥等处载集中。而胜天不能言。盖拟议名号而未及揭版。故不传。然亦不过吾辈筇鞋所及。而非有别区也。夜分欲就睡。忽闻敲门声。呼僧出看。乃晓送人。中途遇官伻。付书回衙。渠便还。追及于此。传家大人赐书。有曰白云固多名胜。且近釜渊,谷云。恐非三日游可了。如有
未可造次寻觅。俄雨复作。衣尽湿。狼狈寻来路还。陟成氏亭。同游皆已避雨登憩矣。亭在瀑东不十步。而颇爽豁可人意。书生数三辈读于其中。乞铁铛煖酒相属。凭轩望弼云山色。晡时乍晴。则疾驱过叠石。薄暮始入华阴洞口。先寻谷云翁遗祠。拜画真。登笼水亭。读尤庵所撰碑记。先遣仆马就伴睡庵炊秣。负策随其后。庵去洞口甚遥以隩。屡憩屡起。钟鸣时才及寺门。道侧林樾间。隐隐见亭台缥缈。而皆未遑跻攀。俟明日一纵目焉。有十馀僧皆能识字。又喜谈山说水。应对如响。小沙弥智行尤清敏可爱。携灯邀客。至其房指阁中梅曰此先生旧梅也。僧等共养护之。犹待先生也。此间人皆称渊翁为进士先生云。是日金尊父为检渊翁遗草。来住下村。(三渊故宅。)因胜天相闻。借谷云集来。其记华岳名胜甚详。与闻诸胜天者。一一相符。但所谓表独立台,逍遥游堂,閒来往桥等处载集中。而胜天不能言。盖拟议名号而未及揭版。故不传。然亦不过吾辈筇鞋所及。而非有别区也。夜分欲就睡。忽闻敲门声。呼僧出看。乃晓送人。中途遇官伻。付书回衙。渠便还。追及于此。传家大人赐书。有曰白云固多名胜。且近釜渊,谷云。恐非三日游可了。如有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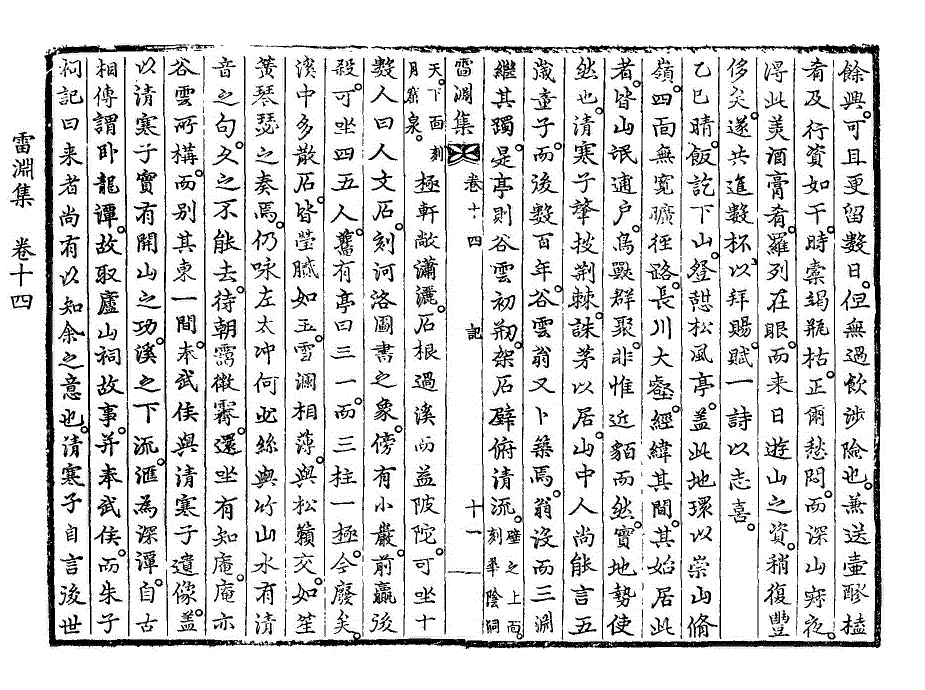 馀兴。可且更留数日。但无过饮涉险也。兼送壶醪榼肴及行资如干。时橐竭瓶枯。正尔愁闷。而深山寂夜。得此美酒膏肴。罗列在眼。而来日游山之资。稍复丰侈矣。遂共进数杯以拜赐。赋一诗以志喜。
馀兴。可且更留数日。但无过饮涉险也。兼送壶醪榼肴及行资如干。时橐竭瓶枯。正尔愁闷。而深山寂夜。得此美酒膏肴。罗列在眼。而来日游山之资。稍复丰侈矣。遂共进数杯以拜赐。赋一诗以志喜。乙巳晴。饭讫下山。登憩松风亭。盖此地环以崇山脩岭。四面无宽旷径路。长川大壑。经纬其间。其始居此者。皆山氓逋户。鸟兽群聚。非惟近貊而然。实地势使然也。清寒子肇披荆棘。诛茅以居。山中人尚能言五岁童子。而后数百年。谷云翁又卜筑焉。翁没而三渊继其躅。是亭则谷云初刱。架石壁俯清流。(壁之上面。刻华阴洞天。下面刻月窟泉。)极轩敞潇洒。石根过溪而益陂陀。可坐十数人曰人文石。刻河洛图书之象。傍有小岩。前赢后杀。可坐四五人。旧有亭曰三一。而三柱一极。今废矣。溪中多散石。皆莹腻如玉。雪澜相薄。与松籁交。如笙簧琴瑟之奏焉。仍咏左太冲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之句。久之不能去。待朝霭微霁。还坐有知庵。庵亦谷云所构。而别其东一间。奉武侯与清寒子遗像。盖以清寒子实有开山之功。溪之下流。汇为深潭。自古相传谓卧龙潭。故取庐山祠故事。并奉武侯。而朱子祠记曰来者尚有以知余之意也。清寒子自言后世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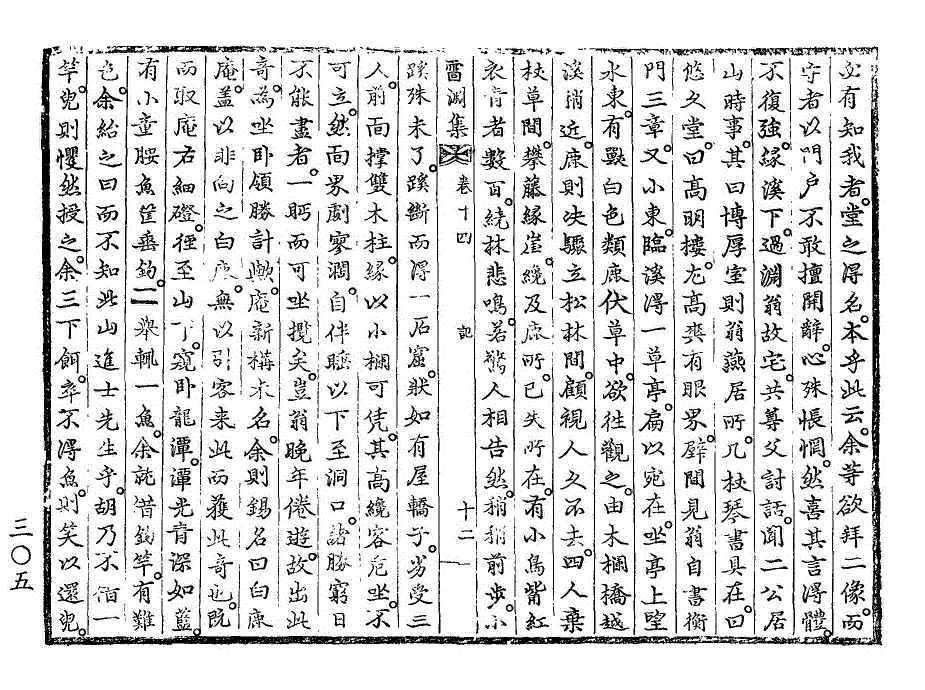 必有知我者。堂之得名。本乎此云。余等欲拜二像。而守者以门户不敢擅开辞。心殊怅惘。然喜其言得体。不复强。缘溪下。过渊翁故宅。共尊父讨话。闻二公居山时事。其曰博厚室则翁燕居所。几杖琴书具在。曰悠久堂。曰高明楼。尤高爽有眼界。壁间见翁自书衡门三章。又小东。临溪得一草亭。扁以宛在。坐亭上望水东。有兽白色类鹿伏草中。欲往观之。由木栏桥越溪稍近。鹿则决骤立松林间。顾视人久不去。四人弃杖草间。攀藤缘崖。才及鹿所。已失所在。有小鸟觜红衣青者数百。绕林悲鸣。若惊人相告然。稍稍前步。小蹊殊未了。蹊断而得一石窟。状如有屋轿子。劣受三人。前面撑双木柱。缘以小栏可凭。其高才容危坐。不可立。然面界剧寥阔。自伴睡以下至洞口。诸胜穷日不能尽者。一眄而可坐揽矣。岂翁晚年倦游。故出此奇。为坐卧领胜计欤。庵新构未名。余则锡名曰白鹿庵。盖以非向之白鹿。无以引客来此而获此奇也。既而取庵右细磴。径至山下。窥卧龙潭。潭光青深如蓝。有小童腰鱼筐垂钓。二举辄一鱼。余就借钓竿。有难色。余绐之曰而不知此山进士先生乎。胡乃不借一竿。儿则戄然授之。余三下饵。卒不得鱼。则笑以还儿。
必有知我者。堂之得名。本乎此云。余等欲拜二像。而守者以门户不敢擅开辞。心殊怅惘。然喜其言得体。不复强。缘溪下。过渊翁故宅。共尊父讨话。闻二公居山时事。其曰博厚室则翁燕居所。几杖琴书具在。曰悠久堂。曰高明楼。尤高爽有眼界。壁间见翁自书衡门三章。又小东。临溪得一草亭。扁以宛在。坐亭上望水东。有兽白色类鹿伏草中。欲往观之。由木栏桥越溪稍近。鹿则决骤立松林间。顾视人久不去。四人弃杖草间。攀藤缘崖。才及鹿所。已失所在。有小鸟觜红衣青者数百。绕林悲鸣。若惊人相告然。稍稍前步。小蹊殊未了。蹊断而得一石窟。状如有屋轿子。劣受三人。前面撑双木柱。缘以小栏可凭。其高才容危坐。不可立。然面界剧寥阔。自伴睡以下至洞口。诸胜穷日不能尽者。一眄而可坐揽矣。岂翁晚年倦游。故出此奇。为坐卧领胜计欤。庵新构未名。余则锡名曰白鹿庵。盖以非向之白鹿。无以引客来此而获此奇也。既而取庵右细磴。径至山下。窥卧龙潭。潭光青深如蓝。有小童腰鱼筐垂钓。二举辄一鱼。余就借钓竿。有难色。余绐之曰而不知此山进士先生乎。胡乃不借一竿。儿则戄然授之。余三下饵。卒不得鱼。则笑以还儿。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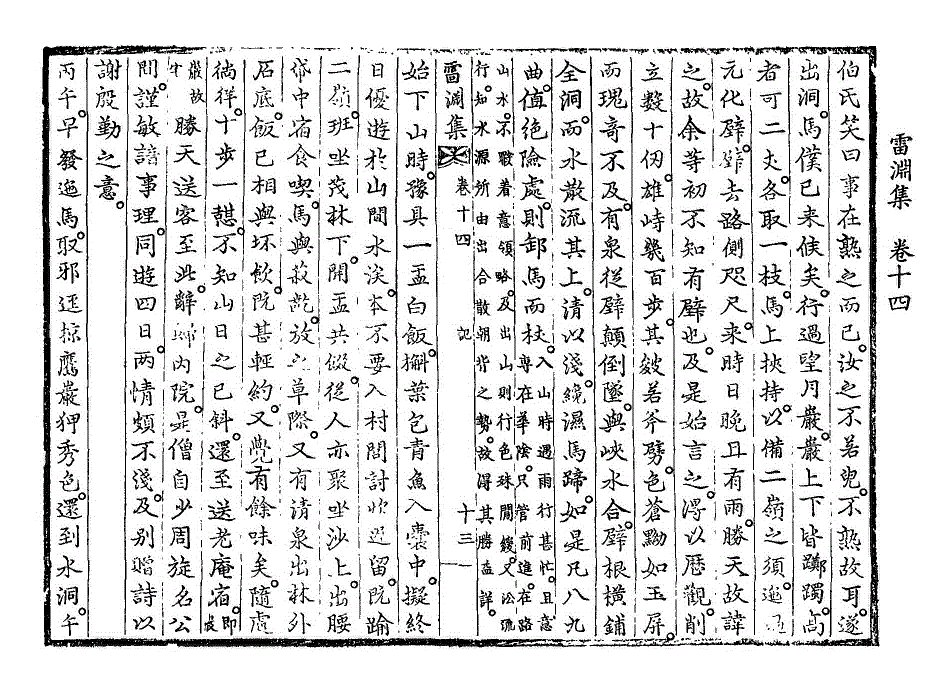 伯氏笑曰事在熟之而已。汝之不若儿。不熟故耳。遂出洞。马仆已来候矣。行过望月岩。岩上下皆踯躅。高者可二丈。各取一枝。马上挟持。以备二岭之须。迤过元化壁。壁去路侧咫尺。来时日晚且有雨。胜天故讳之。故余等初不知有壁也。及是始言之。得以历观。削立数十仞。雄峙几百步。其皴若斧劈。色苍黝如玉屏。而瑰奇不及。有泉从壁颠倒坠。与峡水合。壁根横铺全洞。而水散流其上。清以浅。才湿马蹄。如是凡八九曲。值绝险处。则卸马而杖。(入山时遇雨行甚忙。且意专在华阴。只管前进。在路山水。不暇着意领略。及出山则行色殊閒缓。又沿流行。知水源所由出合散朝背之势。故得其胜益详。)始下山时。豫具一盂白饭。槲叶包青鱼入囊中。拟终日优游于山间水涘。本不要入村闾讨炊迟留。既踰二岭。班坐茂林下。开盂共啜。从人亦聚坐沙上。出腰袋中宿食吃。马与菽龁。放之草际。又有清泉出林外石底。饭已相与坏饮。既甚轻约。又觉有馀味矣。随处徜徉。十步一憩。不知山日之已斜。还至送老庵宿。(即农岩故宅。)胜天送客至此。辞归内院。是僧自少周旋名公间。谨敏谙事理。同游四日。两情颇不浅。及别赠诗以谢殷勤之意。
伯氏笑曰事在熟之而已。汝之不若儿。不熟故耳。遂出洞。马仆已来候矣。行过望月岩。岩上下皆踯躅。高者可二丈。各取一枝。马上挟持。以备二岭之须。迤过元化壁。壁去路侧咫尺。来时日晚且有雨。胜天故讳之。故余等初不知有壁也。及是始言之。得以历观。削立数十仞。雄峙几百步。其皴若斧劈。色苍黝如玉屏。而瑰奇不及。有泉从壁颠倒坠。与峡水合。壁根横铺全洞。而水散流其上。清以浅。才湿马蹄。如是凡八九曲。值绝险处。则卸马而杖。(入山时遇雨行甚忙。且意专在华阴。只管前进。在路山水。不暇着意领略。及出山则行色殊閒缓。又沿流行。知水源所由出合散朝背之势。故得其胜益详。)始下山时。豫具一盂白饭。槲叶包青鱼入囊中。拟终日优游于山间水涘。本不要入村闾讨炊迟留。既踰二岭。班坐茂林下。开盂共啜。从人亦聚坐沙上。出腰袋中宿食吃。马与菽龁。放之草际。又有清泉出林外石底。饭已相与坏饮。既甚轻约。又觉有馀味矣。随处徜徉。十步一憩。不知山日之已斜。还至送老庵宿。(即农岩故宅。)胜天送客至此。辞归内院。是僧自少周旋名公间。谨敏谙事理。同游四日。两情颇不浅。及别赠诗以谢殷勤之意。丙午。早发迤马。取邪径掠鹰岩狎秀色。还到水洞。午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6L 页
 饭驰归县衙。日未夕矣。
饭驰归县衙。日未夕矣。戊申。访青鹤洞。游者五人。盖郑生尚伯(即国宾同游玉屏者)新来从之也。洞去县门十数里。雅以形胜称。至目击。大负所闻。水无萦回之态。山无峭秀之气。又无茂林幽泉可以漱濯攀援。特一懒山。带一无情水耳。谂洞名之义于尚伯。其对类七仙之对。荒唐不可述。宗之甚捷。遇水辄跳过。伯氏,文远亦次第过去。余独不能。拾石为梁而后乃渡。宗之甚迟之。常号余为滞瀑仙。又自号飞瀑仙以为戏。是游也。拈韵得仙字。将赋有白鳖入渔人之笱。宗之欲见之。跳过水南。苔滑石仄。遂溺焉。衣巾尽湿。余就而劳之。仍得一句曰仙人青鹤归何处。飞瀑仙为落瀑仙。一座粲然大噱。归路游乐归亭。则芝川黄公所栖止也。杜鹃笼山烂开。照映一溪。游人渔子都在锦绣屏中。甚奇观也。
辛亥。余与宗之将还洛。既辞亲前。退至草堂则伯氏及文远因要游白鹭洲。洲去县门十里近。在走洛道傍。地势颇旷豁。不似峡中。而山水至此。却散缓平铺。水中多穹石。众流激射萦折而行。沙砾为湍头陶汰。堆一边如积雪。苍岩蜿蜒入水心特起。水触之。遂分二派。左右而流。洲名盖取太白诗二水中分之义也。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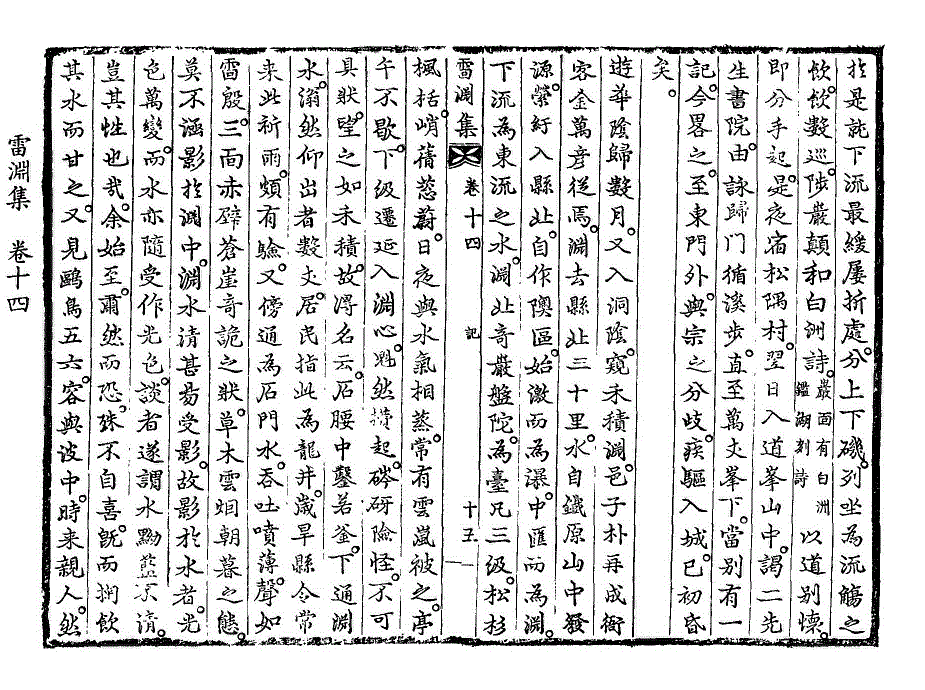 于是就下流最缓屡折处。分上下矶。列坐为流觞之饮。饮数巡。陟岩颠和白洲诗。(岩面有白洲鉴湖刻诗。)以道别怀。即分手起。是夜宿松隅村。翌日入道峰山中。谒二先生书院。由咏归门循溪步。直至万丈峰下。当别有一记。今略之。至东门外。与宗之分歧。疾驱入城。已初昏矣。
于是就下流最缓屡折处。分上下矶。列坐为流觞之饮。饮数巡。陟岩颠和白洲诗。(岩面有白洲鉴湖刻诗。)以道别怀。即分手起。是夜宿松隅村。翌日入道峰山中。谒二先生书院。由咏归门循溪步。直至万丈峰下。当别有一记。今略之。至东门外。与宗之分歧。疾驱入城。已初昏矣。游华阴归数月。又入洞阴。窥禾积渊。邑子朴再成衙客金万彦从焉。渊去县北三十里。水自铁原山中发源。萦纡入县北。自作隩区。始激而为瀑。中汇而为渊。下流为东流之水。渊北奇岩盘陀。为台凡三级。松杉枫栝。峭茜葱蔚。日夜与水气相蒸。常有云岚被之。亭午不歇。下级迁延入渊心。魁然攒起。碜砑险怪。不可具状。望之如禾积。故得名云。石腰中凿若釜。下通渊水。滃然仰出者数丈。居民指此为龙井。岁旱县令常来此祈雨。颇有验。又傍通为石门水。吞吐喷薄。声如䨓殷。三面赤壁苍崖奇诡之状。草木云烟朝暮之态。莫不涵影于渊中。渊水清甚易受影。故影于水者。光色万变。而水亦随受作光色。谈者遂谓水黝蓝不清。岂其性也哉。余始至。肃然而恐。殊不自喜。既而掬饮其水而甘之。又见鸥鸟五六。容与波中。时来亲人。然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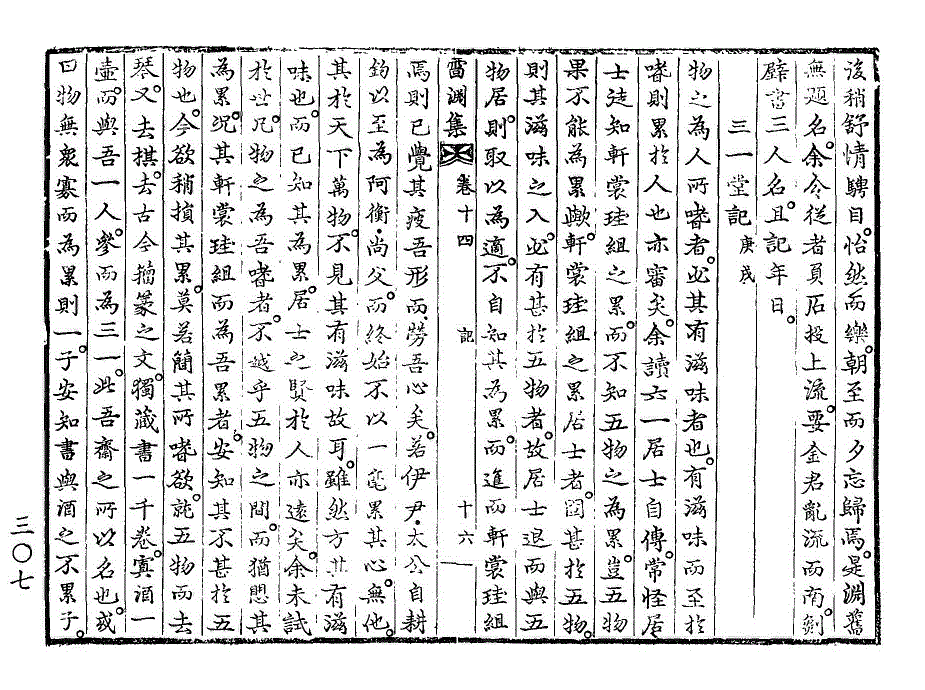 后稍舒情骋目。怡然而乐。朝至而夕忘归焉。是渊旧无题名。余令从者负石投上流。要金君乱流而南。劖壁书三人名。且记年日。
后稍舒情骋目。怡然而乐。朝至而夕忘归焉。是渊旧无题名。余令从者负石投上流。要金君乱流而南。劖壁书三人名。且记年日。三一堂记(庚戌)
物之为人所嗜者。必其有滋味者也。有滋味而至于嗜则累于人也亦审矣。余读六一居士自传。常怪居士徒知轩裳圭组之累。而不知五物之为累。岂五物果不能为累欤。轩裳圭组之累居士者。固甚于五物。则其滋味之入。必有甚于五物者。故居士退而与五物居。则取以为适。不自知其为累。而进而轩裳圭组焉则已觉其疲吾形而劳吾心矣。若伊尹,太公自耕钓以至为阿衡,尚父。而终始不以一毫累其心。无他。其于天下万物。不见其有滋味故耳。虽然方其有滋味也。而已知其为累。居士之贤于人亦远矣。余未试于世。凡物之为吾嗜者。不越乎五物之间。而犹惧其为累。况其轩裳圭组而为吾累者。安知其不甚于五物也。今欲稍损其累。莫若简其所嗜欲。就五物而去琴。又去棋。去古今籀篆之文。独藏书一千卷。寘酒一壶。而与吾一人。参而为三一。此吾斋之所以名也。或曰物无众寡而为累则一。子安知书与酒之不累子。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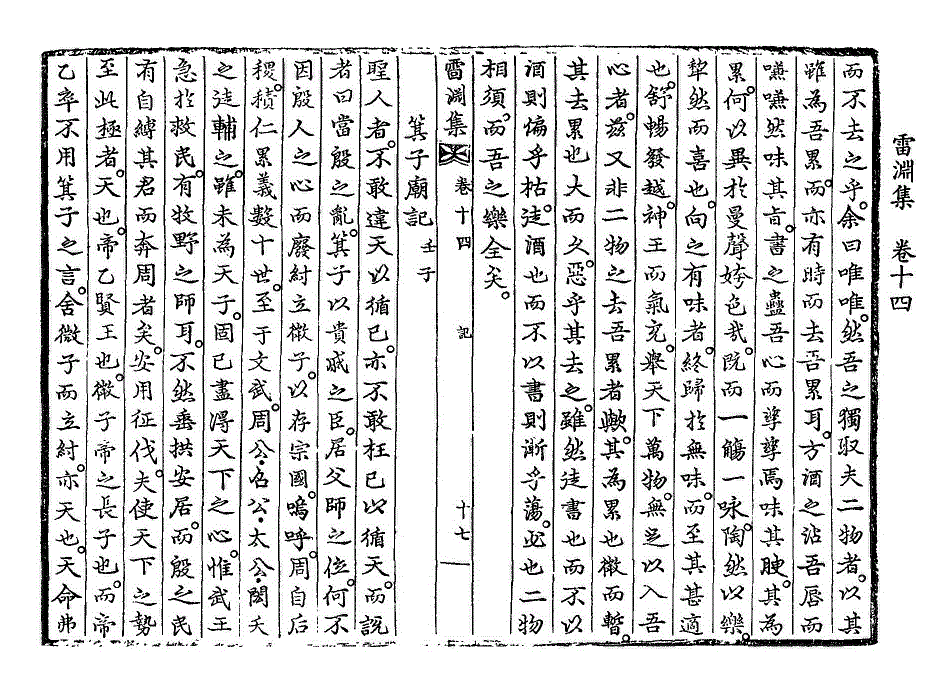 而不去之乎。余曰唯唯。然吾之独取夫二物者。以其虽为吾累。而亦有时而去吾累耳。方酒之沾吾唇而嗛嗛然味其旨。书之蛊吾心而孳孳焉味其腴。其为累。何以异于曼声姱色哉。既而一觞一咏。陶然以乐。犁然而喜也。向之有味者。终归于无味。而至其甚适也。舒畅发越。神王而气充。举天下万物。无足以入吾心者。玆又非二物之去吾累者欤。其为累也微而暂。其去累也大而久。恶乎其去之。虽然徒书也而不以酒则偏乎枯。徒酒也而不以书则渐乎荡。必也二物相须。而吾之乐全矣。
而不去之乎。余曰唯唯。然吾之独取夫二物者。以其虽为吾累。而亦有时而去吾累耳。方酒之沾吾唇而嗛嗛然味其旨。书之蛊吾心而孳孳焉味其腴。其为累。何以异于曼声姱色哉。既而一觞一咏。陶然以乐。犁然而喜也。向之有味者。终归于无味。而至其甚适也。舒畅发越。神王而气充。举天下万物。无足以入吾心者。玆又非二物之去吾累者欤。其为累也微而暂。其去累也大而久。恶乎其去之。虽然徒书也而不以酒则偏乎枯。徒酒也而不以书则渐乎荡。必也二物相须。而吾之乐全矣。箕子庙记(壬子)
圣人者。不敢违天以循己。亦不敢枉己以循天。而说者曰当殷之乱。箕子以贵戚之臣。居父师之位。何不因殷人之心而废纣立微子。以存宗国。呜呼。周自后稷。积仁累义数十世。至于文武。周公,召公,太公,闳夭之徒辅之。虽未为天子。固已尽得天下之心。惟武王急于救民。有牧野之师耳。不然垂拱安居。而殷之民有自缚其君而奔周者矣。安用征伐。夫使天下之势至此极者。天也。帝乙贤王也。微子帝之长子也。而帝乙卒不用箕子之言。舍微子而立纣。亦天也。天命弗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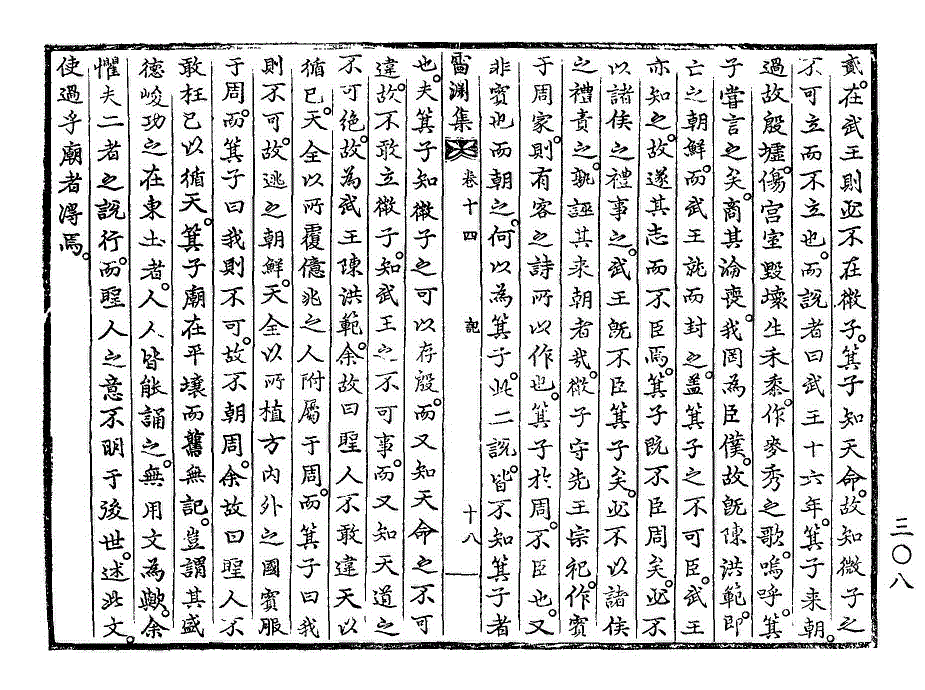 贰。在武王则必不在微子。箕子知天命。故知微子之不可立而不立也。而说者曰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过故殷墟。伤宫室毁坏生禾黍。作麦秀之歌。呜呼。箕子尝言之矣。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故既陈洪范。即亡之朝鲜。而武王就而封之。盖箕子之不可臣。武王亦知之。故遂其志而不臣焉。箕子既不臣周矣。必不以诸侯之礼事之。武王既不臣箕子矣。必不以诸侯之礼责之。孰诬其来朝者哉。微子守先王宗祀。作宾于周家。则有客之诗所以作也。箕子于周。不臣也。又非宾也而朝之。何以为箕子。此二说。皆不知箕子者也。夫箕子知微子之可以存殷。而又知天命之不可违。故不敢立微子。知武王之不可事。而又知天道之不可绝。故为武王陈洪范。余故曰圣人不敢违天以循己。天全以所覆亿兆之人附属于周。而箕子曰我则不可。故逃之朝鲜。天全以所植方内外之国宾服于周。而箕子曰我则不可。故不朝周。余故曰圣人不敢枉己以循天。箕子庙在平壤而旧无记。岂谓其盛德峻功之在东土者。人人皆能诵之。无用文为欤。余惧夫二者之说行。而圣人之意不明于后世。述此文。使过乎庙者得焉。
贰。在武王则必不在微子。箕子知天命。故知微子之不可立而不立也。而说者曰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过故殷墟。伤宫室毁坏生禾黍。作麦秀之歌。呜呼。箕子尝言之矣。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故既陈洪范。即亡之朝鲜。而武王就而封之。盖箕子之不可臣。武王亦知之。故遂其志而不臣焉。箕子既不臣周矣。必不以诸侯之礼事之。武王既不臣箕子矣。必不以诸侯之礼责之。孰诬其来朝者哉。微子守先王宗祀。作宾于周家。则有客之诗所以作也。箕子于周。不臣也。又非宾也而朝之。何以为箕子。此二说。皆不知箕子者也。夫箕子知微子之可以存殷。而又知天命之不可违。故不敢立微子。知武王之不可事。而又知天道之不可绝。故为武王陈洪范。余故曰圣人不敢违天以循己。天全以所覆亿兆之人附属于周。而箕子曰我则不可。故逃之朝鲜。天全以所植方内外之国宾服于周。而箕子曰我则不可。故不朝周。余故曰圣人不敢枉己以循天。箕子庙在平壤而旧无记。岂谓其盛德峻功之在东土者。人人皆能诵之。无用文为欤。余惧夫二者之说行。而圣人之意不明于后世。述此文。使过乎庙者得焉。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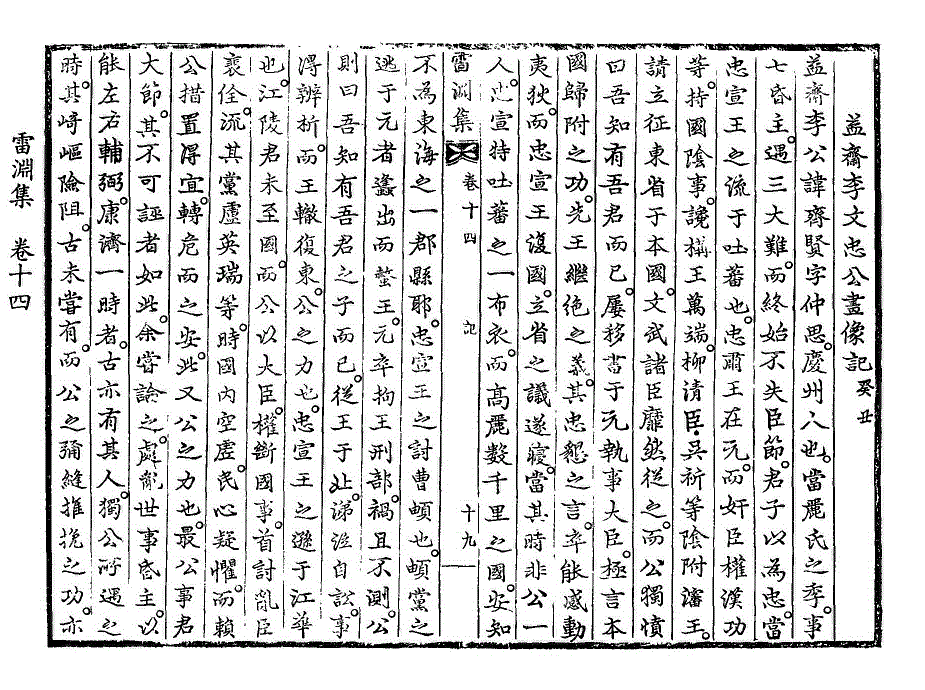 益斋李文忠公画像记(癸丑)
益斋李文忠公画像记(癸丑)益斋李公讳齐贤字仲思。庆州人也。当丽氏之季。事七昏主。遇三大难。而终始不失臣节。君子以为忠。当忠宣王之流于吐蕃也。忠肃王在元。而奸臣权汉功等。持国阴事。谗构王万端。柳清臣,吴祈等阴附沈王。请立征东省于本国。文武诸臣靡然从之。而公独愤曰吾知有吾君而已。屡移书于元执事大臣。极言本国归附之功。先王继绝之义。其忠恳之言。卒能感动夷狄。而忠宣王复国。立省之议遂寝。当其时非公一人。忠宣特吐蕃之一布衣。而高丽数千里之国。安知不为东海之一郡县耶。忠宣王之讨曹頔也。頔党之逃于元者蜂出而螫王。元卒拘王刑部。祸且不测。公则曰吾知有吾君之子而已。从王于北。涕泣自讼。事得辨析。而王辙复东。公之力也。忠宣王之逊于江华也。江陵君未至国。而公以大臣。权断国事。首讨乱臣裴佺。流其党卢英瑞等。时国内空虚。民心疑惧。而赖公措置得宜。转危而之安。此又公之力也。最公事君大节。其不可诬者如此。余尝论之。处乱世事昏主。以能左右辅弼。康济一时者。古亦有其人。独公所遇之时。其崎岖险阻。古未尝有。而公之弥缝推挽之功。亦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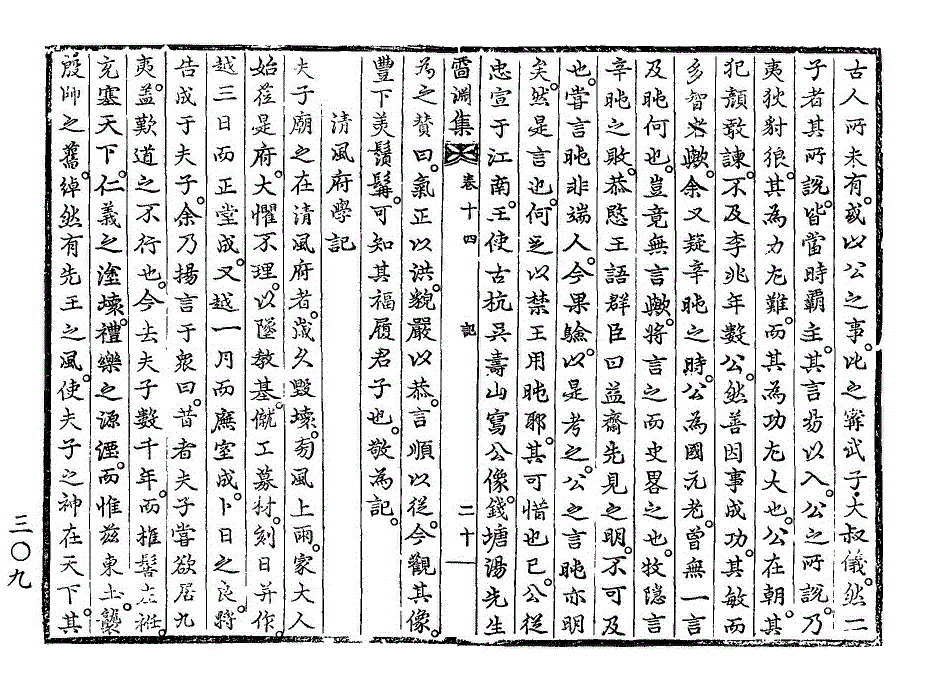 古人所未有。或以公之事。比之宁武子,大叔仪。然二子者其所说。皆当时霸主。其言易以入。公之所说。乃夷狄豺狼。其为力尤难。而其为功尤大也。公在朝。其犯颜敢谏。不及李兆年数公。然善因事成功。其敏而多智欤。余又疑辛旽之时。公为国元老。曾无一言及旽何也。岂竟无言欤。将言之而史略之也。牧隐言辛旽之败。恭悯王语群臣曰益斋先见之明。不可及也。尝言旽非端人。今果验。以是考之。公之言旽亦明矣。然是言也。何足以禁王用旽耶。其可惜也已。公从忠宣于江南。王使古杭吴寿山写公像。钱塘汤先生为之赞曰。气正以洪。貌严以恭。言顺以从。今观其像。丰下美须髯。可知其福履君子也。敬为记。
古人所未有。或以公之事。比之宁武子,大叔仪。然二子者其所说。皆当时霸主。其言易以入。公之所说。乃夷狄豺狼。其为力尤难。而其为功尤大也。公在朝。其犯颜敢谏。不及李兆年数公。然善因事成功。其敏而多智欤。余又疑辛旽之时。公为国元老。曾无一言及旽何也。岂竟无言欤。将言之而史略之也。牧隐言辛旽之败。恭悯王语群臣曰益斋先见之明。不可及也。尝言旽非端人。今果验。以是考之。公之言旽亦明矣。然是言也。何足以禁王用旽耶。其可惜也已。公从忠宣于江南。王使古杭吴寿山写公像。钱塘汤先生为之赞曰。气正以洪。貌严以恭。言顺以从。今观其像。丰下美须髯。可知其福履君子也。敬为记。清风府学记
夫子庙之在清风府者。岁久毁坏。旁风上雨。家大人始莅是府。大惧不理。以坠教基。僦工募材。刻日并作。越三日而正堂成。又越一月而庑室成。卜日之良。将告成于夫子。余乃扬言于众曰。昔者夫子尝欲居九夷。盖叹道之不行也。今去夫子数千年。而椎髻左衽。充塞天下。仁义之涂坏。礼乐之源湮。而惟玆东土。袭殷师之旧。绰然有先王之风。使夫子之神在天下。其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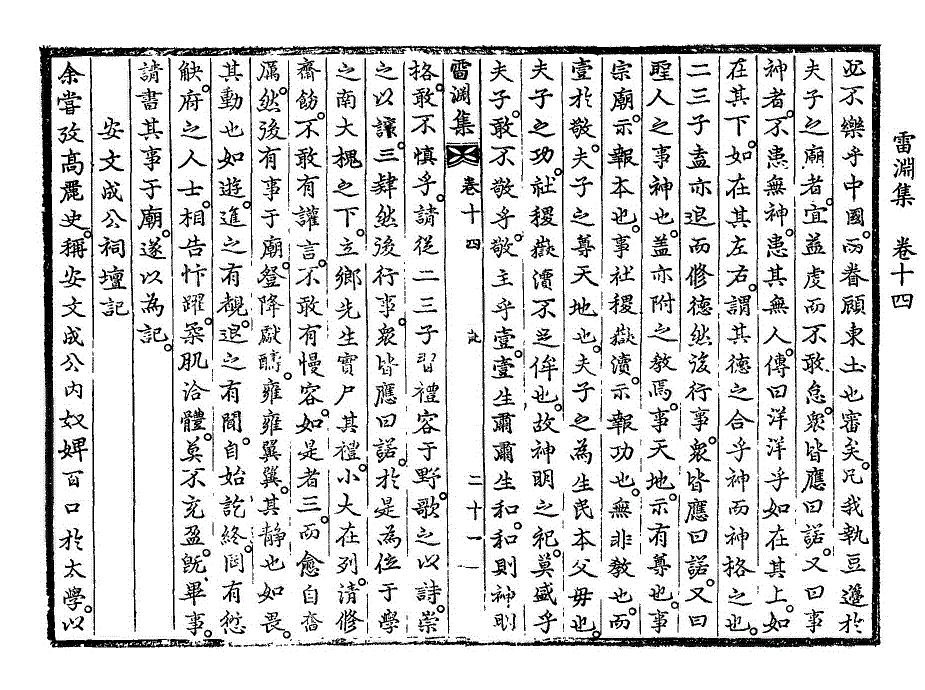 必不乐乎中国。而眷顾东土也审矣。凡我执豆笾于夫子之庙者。宜益虔而不敢怠。众皆应曰诺。又曰事神者。不患无神。患其无人。传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谓其德之合乎神而神格之也。二三子盍亦退而修德然后行事。众皆应曰诺。又曰圣人之事神也。盖亦附之教焉。事天地。示有尊也。事宗庙。示报本也。事社稷岳渎。示报功也。无非教也。而壹于敬。夫子之尊天地也。夫子之为生民本父母也。夫子之功。社稷岳渎不足侔也。故神明之祀。莫盛乎夫子。敢不敬乎。敬主乎壹。壹生肃肃生和。和则神明格。敢不慎乎。请从二三子习礼容于野。歌之以诗。崇之以让。三肄然后行事。众皆应曰诺。于是为位于学之南大槐之下。立乡先生实尸其礼。小大在列。清修斋饬。不敢有欢言。不敢有慢容。如是者三。而愈自奋厉。然后有事于庙。登降献酬。雍雍翼翼。其静也如畏。其动也如游。进之有睹。退之有闻。自始讫终。罔有愆觖。府之人士。相告忭跃。柔肌洽体。莫不充盈。既毕事。请书其事于庙。遂以为记。
必不乐乎中国。而眷顾东土也审矣。凡我执豆笾于夫子之庙者。宜益虔而不敢怠。众皆应曰诺。又曰事神者。不患无神。患其无人。传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谓其德之合乎神而神格之也。二三子盍亦退而修德然后行事。众皆应曰诺。又曰圣人之事神也。盖亦附之教焉。事天地。示有尊也。事宗庙。示报本也。事社稷岳渎。示报功也。无非教也。而壹于敬。夫子之尊天地也。夫子之为生民本父母也。夫子之功。社稷岳渎不足侔也。故神明之祀。莫盛乎夫子。敢不敬乎。敬主乎壹。壹生肃肃生和。和则神明格。敢不慎乎。请从二三子习礼容于野。歌之以诗。崇之以让。三肄然后行事。众皆应曰诺。于是为位于学之南大槐之下。立乡先生实尸其礼。小大在列。清修斋饬。不敢有欢言。不敢有慢容。如是者三。而愈自奋厉。然后有事于庙。登降献酬。雍雍翼翼。其静也如畏。其动也如游。进之有睹。退之有闻。自始讫终。罔有愆觖。府之人士。相告忭跃。柔肌洽体。莫不充盈。既毕事。请书其事于庙。遂以为记。安文成公祠坛记
余尝考高丽史。称安文成公内奴婢百口于太学。以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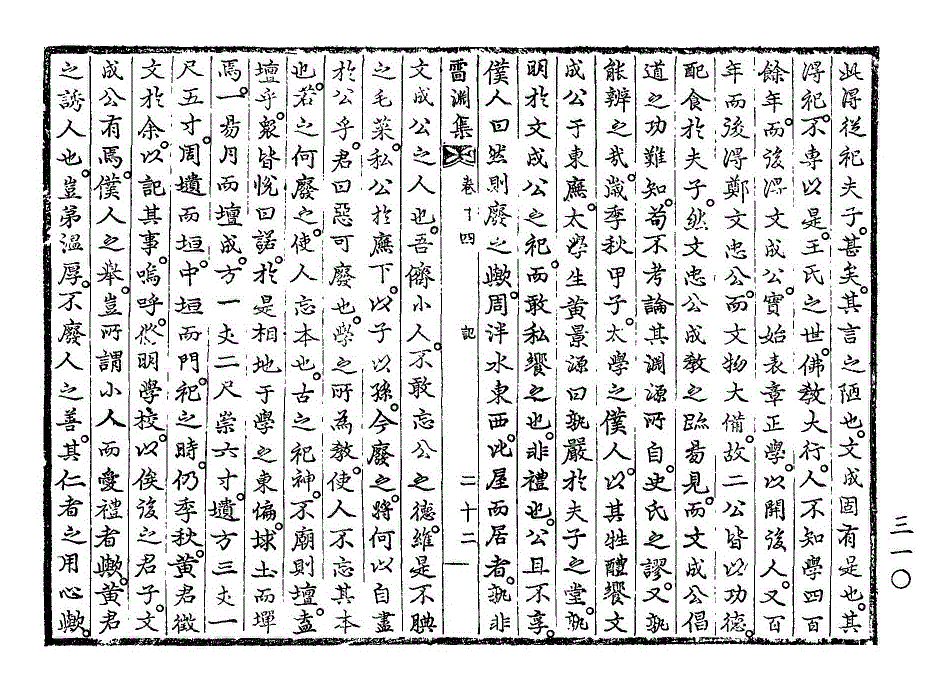 此得从祀夫子。甚矣。其言之陋也。文成固有是也。其得祀。不专以是。王氏之世。佛教大行。人不知学四百馀年。而后得文成公。实始表章正学。以开后人。又百年而后得郑文忠公。而文物大备。故二公皆以功德。配食于夫子。然文忠公成教之迹易见。而文成公倡道之功难知。苟不考论其渊源所自。史氏之谬。又孰能辨之哉。岁季秋甲子。太学之仆人。以其牲醴飨文成公于东庑。太学生黄景源曰孰严于夫子之堂。孰明于文成公之祀。而敢私飨之也。非礼也。公且不享。仆人曰然则废之欤。周泮水东西。比屋而居者。孰非文成公之人也。吾侪小人。不敢忘公之德。维是不腆之毛菜。私公于庑下。以子以孙。今废之。将何以自尽于公乎。君曰恶可废也。学之所为教。使人不忘其本也。若之何废之。使人忘本也。古之祀神。不庙则坛。盍坛乎。众皆悦曰诺。于是相地于学之东偏。𡌋土而墠焉。一易月而坛成。方一丈二尺崇六寸。壝方三丈一尺五寸。周壝而垣。中垣而门。祀之时。仍季秋。黄君徵文于余。以记其事。呜呼。修明学校。以俟后之君子。文成公有焉。仆人之举。岂所谓小人而爱礼者欤。黄君之诱人也。岂弟温厚。不废人之善。其仁者之用心欤。
此得从祀夫子。甚矣。其言之陋也。文成固有是也。其得祀。不专以是。王氏之世。佛教大行。人不知学四百馀年。而后得文成公。实始表章正学。以开后人。又百年而后得郑文忠公。而文物大备。故二公皆以功德。配食于夫子。然文忠公成教之迹易见。而文成公倡道之功难知。苟不考论其渊源所自。史氏之谬。又孰能辨之哉。岁季秋甲子。太学之仆人。以其牲醴飨文成公于东庑。太学生黄景源曰孰严于夫子之堂。孰明于文成公之祀。而敢私飨之也。非礼也。公且不享。仆人曰然则废之欤。周泮水东西。比屋而居者。孰非文成公之人也。吾侪小人。不敢忘公之德。维是不腆之毛菜。私公于庑下。以子以孙。今废之。将何以自尽于公乎。君曰恶可废也。学之所为教。使人不忘其本也。若之何废之。使人忘本也。古之祀神。不庙则坛。盍坛乎。众皆悦曰诺。于是相地于学之东偏。𡌋土而墠焉。一易月而坛成。方一丈二尺崇六寸。壝方三丈一尺五寸。周壝而垣。中垣而门。祀之时。仍季秋。黄君徵文于余。以记其事。呜呼。修明学校。以俟后之君子。文成公有焉。仆人之举。岂所谓小人而爱礼者欤。黄君之诱人也。岂弟温厚。不废人之善。其仁者之用心欤。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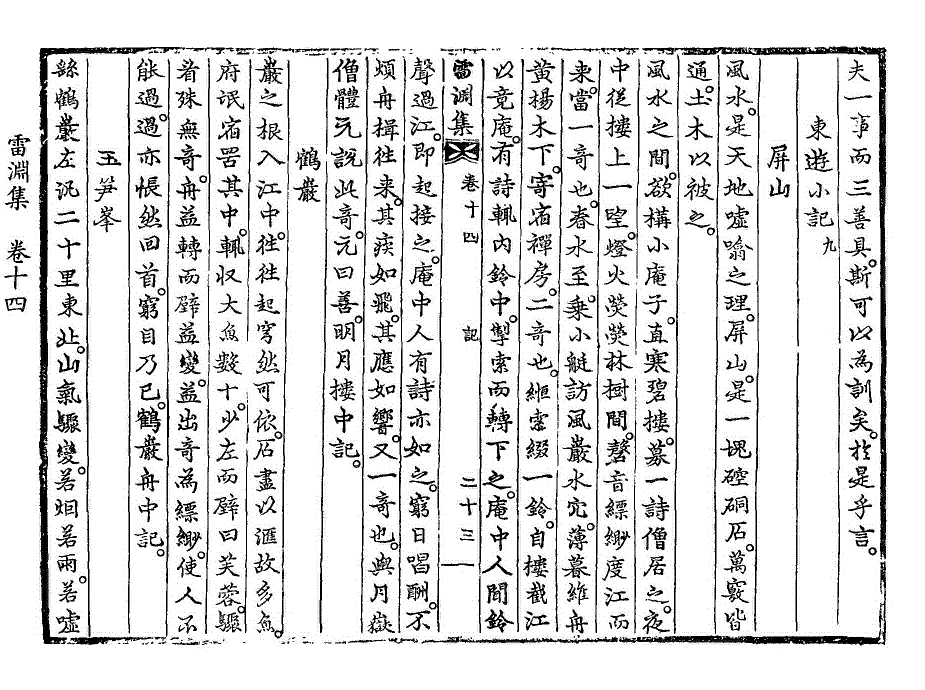 夫一事而三善具。斯可以为训矣。于是乎言。
夫一事而三善具。斯可以为训矣。于是乎言。东游小记(九)
屏山
风水。是天地嘘噏之理。屏山。是一块硿硐石。万窍皆通。土木以被之。
风水之间。欲构小庵子。直寒碧楼。募一诗僧居之。夜中从楼上一望。灯火荧荧林树间。磬音缥缈度江而来。当一奇也。春水至。乘小艇访风岩水穴。薄暮维舟黄杨木下。寄宿禅房。二奇也。縆索缀一铃。自楼截江以竟庵。有诗辄内铃中。掣索而转下之。庵中人闻铃声过江。即起接之。庵中人有诗亦如之。穷日唱酬。不烦舟楫往来。其疾如飞。其应如响。又一奇也。与月岳僧体元说此奇。元曰善。明月楼中记。
鹤岩
岩之根入江中。往往起穹然可依。石尽以汇故多鱼。府氓宿罟其中。辄收大鱼数十。少左而壁曰芙蓉。骤看殊无奇。舟益转而壁益变。益出奇为缥缈。使人不能过。过亦怅然回首。穷目乃已。鹤岩舟中记。
玉笋峰
繇鹤岩左汎二十里东北。山气骤变。若烟若雨。若嘘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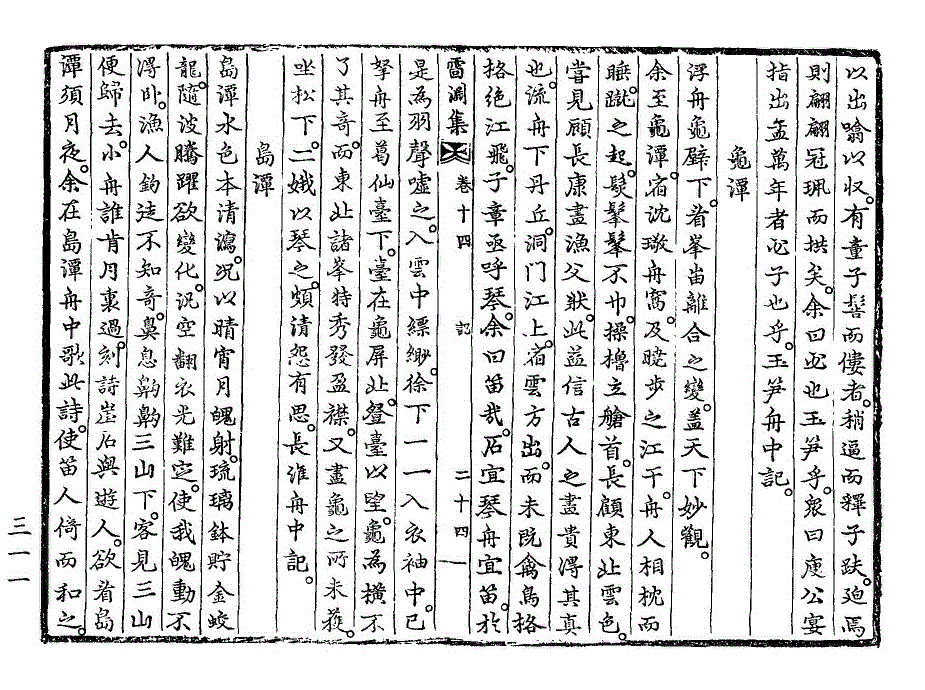 以出噏以收。有童子髻而偻者。稍逼而释子趺。迫焉则翩翩冠佩而拱矣。余曰必也玉笋乎。众曰庾公宴指出孟万年者必子也乎。玉笋舟中记。
以出噏以收。有童子髻而偻者。稍逼而释子趺。迫焉则翩翩冠佩而拱矣。余曰必也玉笋乎。众曰庾公宴指出孟万年者必子也乎。玉笋舟中记。龟潭
浮舟龟壁下。看峰岫离合之变。盖天下妙观。
余至龟潭。宿沈璥舟窝。及晓步之江干。舟人相枕而睡。蹴之起。发髼髼不巾。操橹立舱首。长顾东北云色。尝见顾长康画渔父状。此益信古人之画贵得其真也。流舟下丹丘。洞门江上。宿云方出。而未既禽鸟格格绝江飞。子章亟呼琴。余曰笛哉。石宜琴舟宜笛。于是为羽声嘘之。入云中缥缈。徐下一一入衣袖中。已拿舟至葛仙台下。台在龟屏北。登台以望。龟为横不了其奇。而东北诸峰特秀发盈襟。又尽龟之所未获。坐松下。二娥以琴之。颇清怨有思。长淮舟中记。
岛潭
岛潭水色本清泻。况以晴宵月魄射。琉璃钵贮金蛟龙。随波腾跃欲变化。汎空翻衣光难定。使我魄动不得卧。渔人钓徒不知奇。鼻息齁齁三山下。客见三山便归去。小舟谁肯月里过。刻诗崖石与游人。欲看岛潭须月夜。余在岛潭舟中歌此诗。使笛人倚而和之。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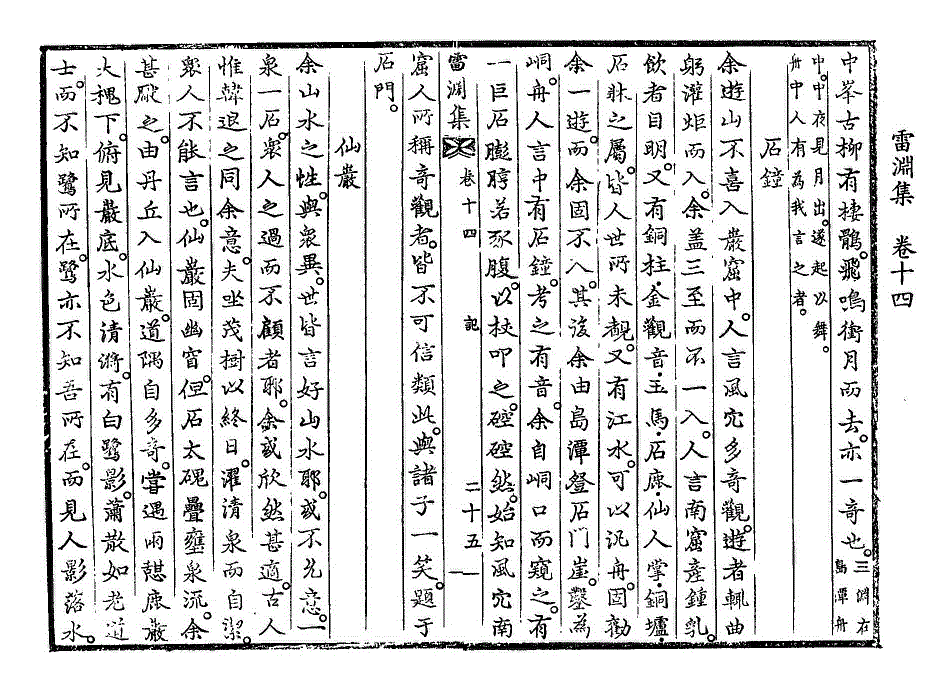 中峰古柳有栖鹘。飞鸣冲月而去。亦一奇也。(三渊在岛潭舟中。中夜见月出。遂起以舞。舟中人有为我言之者。)
中峰古柳有栖鹘。飞鸣冲月而去。亦一奇也。(三渊在岛潭舟中。中夜见月出。遂起以舞。舟中人有为我言之者。)石钟
余游山不喜入岩窟中。人言风穴多奇观。游者辄曲躬灌炬而入。余盖三至而不一入。人言南窟产钟乳。饮者目明。又有铜柱,金观音,玉马,石鹿,仙人掌,铜垆,石床之属。皆人世所未睹。又有江水。可以汎舟。固劝余一游。而余固不入。其后余由岛潭登石门崖。凿为峒。舟人言中有石钟。考之有音。余自峒口而窥之。有一巨石膨脝若豕腹。以杖叩之。硿硿然。始知风穴南窟人所称奇观者。皆不可信类此。与诸子一笑。题于石门。
仙岩
余山水之性。与众异。世皆言好山水耶。或不允意。一泉一石。众人之过而不顾者耶。余或欣然甚适。古人惟韩退之同余意。夫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而自洁。众人不能言也。仙岩固幽窅。但石太磈叠壅泉流。余甚厌之。由丹丘入仙岩。道隅自多奇。尝遇雨憩鹿岩大槐下。俯见岩底。水色清漪。有白鹭影。萧散如老道士。而不知鹭所在。鹭亦不知吾所在。而见人影落水。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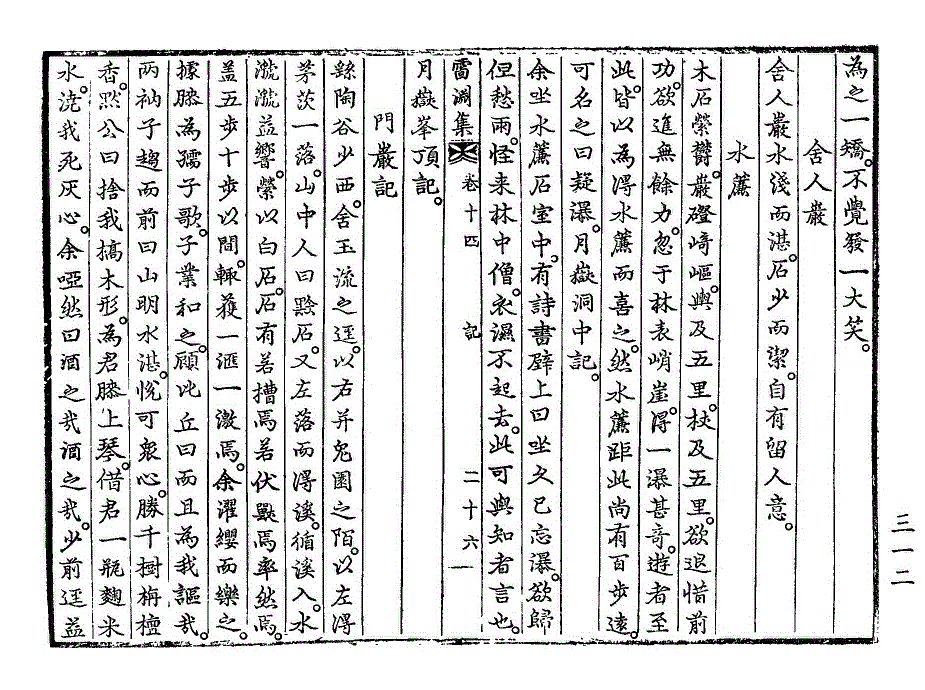 为之一矫。不觉发一大笑。
为之一矫。不觉发一大笑。舍人岩
舍人岩水浅而湛。石少而洁。自有留人意。
水帘
木石萦郁。岩磴崎岖。舆及五里。杖及五里。欲退惜前功。欲进无馀力。忽于林表峭崖。得一瀑甚奇。游者至此。皆以为得水帘而喜之。然水帘距此尚有百步远。可名之曰疑瀑。月岳洞中记。
余坐水帘石室中。有诗书壁上曰坐久已忘瀑。欲归但愁雨。怪来林中僧。衣湿不起去。此可与知者言也。月岳峰顶记。
门岩记
繇陶谷少西。舍玉流之径。以右并兔园之陌。以左得茅茨一落。山中人曰黔石。又左落而得溪。循溪入。水㶁㶁益响。萦以白石。石有若槽焉若伏兽焉率然焉。盖五步十步以间。辄获一汇一激焉。余濯缨而乐之。据膝为孺子歌。子业和之。顾比丘曰而且为我讴哉。两衲子趋而前曰山明水湛。悦可众心。胜千树栴檀香。默公曰舍我槁木形。为君膝上琴。借君一瓶曲米水。浇我死灰心。余哑然曰酒之哉酒之哉。少前径益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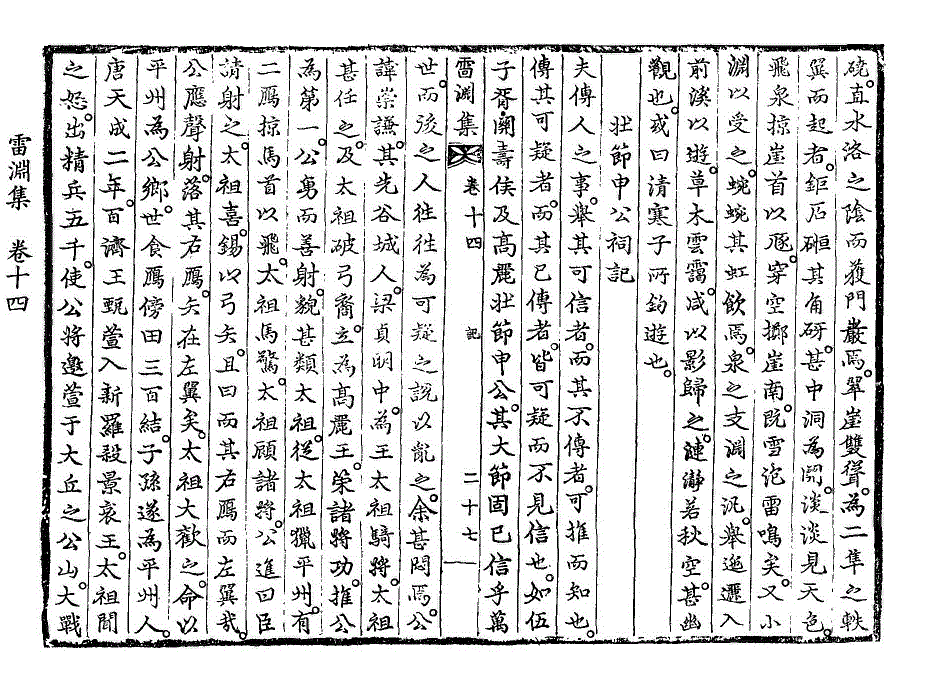 硗。直水洛之阴而获门岩焉。翠崖双耸。为二隼之轶翼而起者。钜石
硗。直水洛之阴而获门岩焉。翠崖双耸。为二隼之轶翼而起者。钜石壮节申公祠记
夫传人之事。举其可信者。而其不传者。可推而知也。传其可疑者。而其已传者。皆可疑而不见信也。如伍子胥,关寿侯及高丽壮节申公。其大节固已信乎万世。而后之人往往为可疑之说以乱之。余甚闷焉。公讳崇谦。其先谷城人。梁贞明中。为王太祖骑将。太祖甚任之。及太祖破弓裔。立为高丽王。策诸将功。推公为第一。公勇而善射。貌甚类太祖。从太祖猎平州。有二雁掠马首以飞。太祖马惊。太祖顾诸将。公进曰臣请射之。太祖喜。锡以弓矢。且曰而其右雁而左翼哉。公应声射。落其右雁。矢在左翼矣。太祖大欢之。命以平州为公乡。世食雁傍田三百结。子孙遂为平州人。唐天成二年。百济王甄萱入新罗杀景哀王。太祖闻之怒。出精兵五千。使公将邀萱于大丘之公山。大战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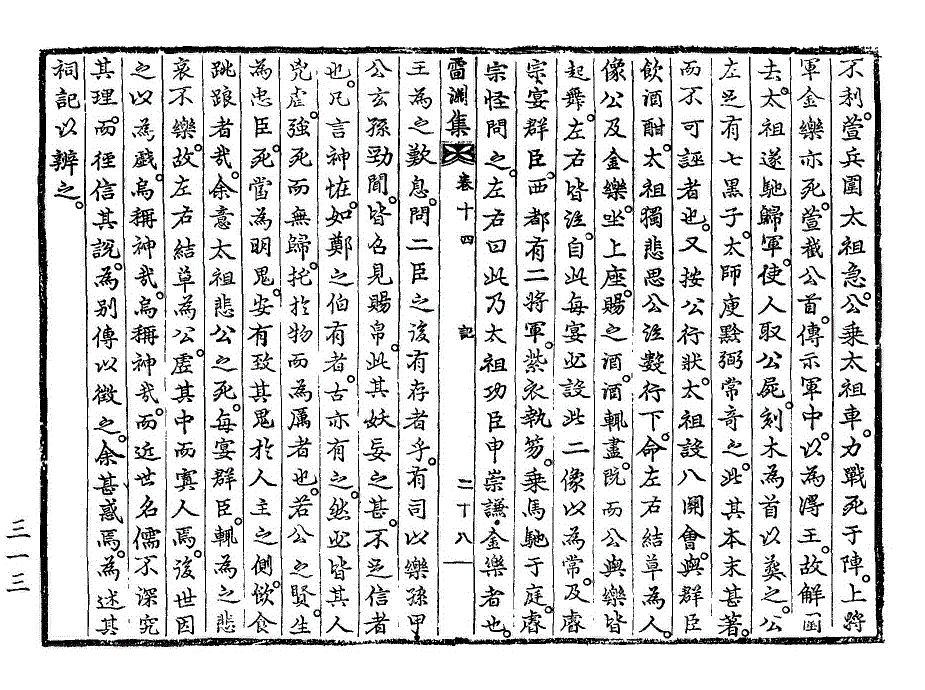 不利。萱兵围太祖急。公乘太祖车。力战死于阵。上将军金乐亦死。萱截公首。传示军中。以为得王。故解围去。太祖遂驰归军。使人取公尸。刻木为首以葬之。公左足有七黑子。太师庾黔弼常奇之。此其本末甚著。而不可诬者也。又按公行状。太祖设八关会。与群臣饮酒酣。太祖独悲思公泣数行下。命左右结草为人。像公及金乐。坐上座。赐之酒。酒辄尽。既而公与乐皆起舞。左右皆泣。自此每宴必设此二像以为常。及睿宗宴群臣。西都有二将军。紫衣执笏。乘马驰于庭。睿宗怪问之。左右曰此乃太祖功臣申崇谦,金乐者也。王为之叹息。问二臣之后有存者乎。有司以乐孙甲,公玄孙劲闻。皆召见赐帛。此其妖妄之甚。不足信者也。凡言神怪。如郑之伯有者。古亦有之。然必皆其人凶虐。强死而无归。托于物而为厉者也。若公之贤。生为忠臣。死当为明鬼。安有致其鬼于人主之侧。饮食跳踉者哉。余意太祖悲公之死。每宴群臣。辄为之悲哀不乐。故左右结草为公。虚其中而寘人焉。后世因之以为戏。乌称神哉。乌称神哉。而近世名儒不深究其理。而径信其说。为别传以徵之。余甚惑焉。为述其祠记以辨之。
不利。萱兵围太祖急。公乘太祖车。力战死于阵。上将军金乐亦死。萱截公首。传示军中。以为得王。故解围去。太祖遂驰归军。使人取公尸。刻木为首以葬之。公左足有七黑子。太师庾黔弼常奇之。此其本末甚著。而不可诬者也。又按公行状。太祖设八关会。与群臣饮酒酣。太祖独悲思公泣数行下。命左右结草为人。像公及金乐。坐上座。赐之酒。酒辄尽。既而公与乐皆起舞。左右皆泣。自此每宴必设此二像以为常。及睿宗宴群臣。西都有二将军。紫衣执笏。乘马驰于庭。睿宗怪问之。左右曰此乃太祖功臣申崇谦,金乐者也。王为之叹息。问二臣之后有存者乎。有司以乐孙甲,公玄孙劲闻。皆召见赐帛。此其妖妄之甚。不足信者也。凡言神怪。如郑之伯有者。古亦有之。然必皆其人凶虐。强死而无归。托于物而为厉者也。若公之贤。生为忠臣。死当为明鬼。安有致其鬼于人主之侧。饮食跳踉者哉。余意太祖悲公之死。每宴群臣。辄为之悲哀不乐。故左右结草为公。虚其中而寘人焉。后世因之以为戏。乌称神哉。乌称神哉。而近世名儒不深究其理。而径信其说。为别传以徵之。余甚惑焉。为述其祠记以辨之。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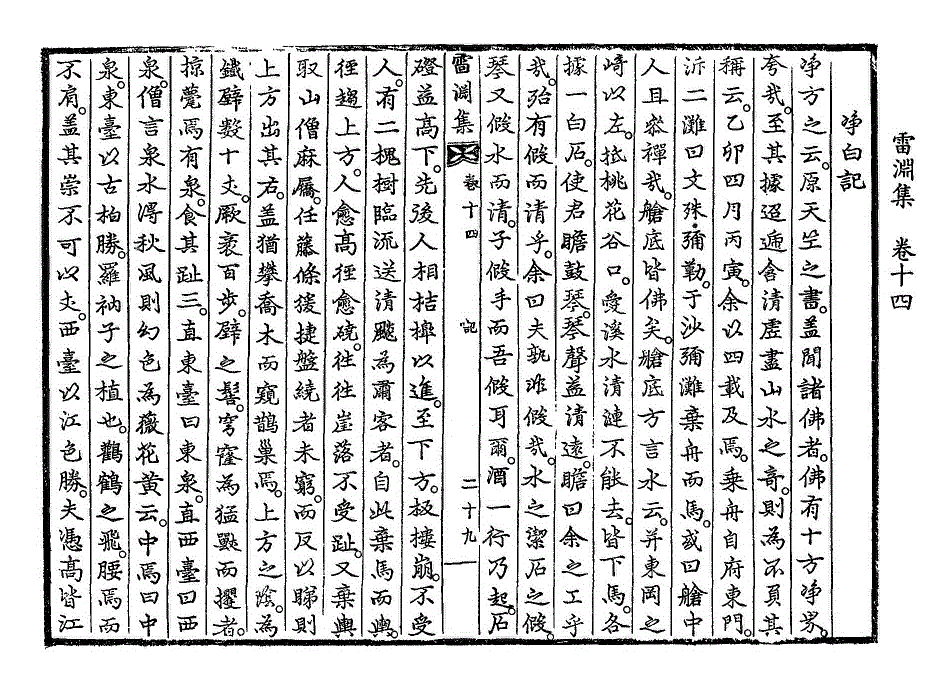 净白记
净白记净方之云。原天竺之书。盖闻诸佛者。佛有十方净界。夸哉。至其据迢递含清虚尽山水之奇。则为不负其称云。乙卯四月丙寅。余以四载及焉。乘舟自府东门。溯二滩曰文殊,弥勒。于沙弥滩弃舟而马。或曰舱中人且参禅哉。舱底皆佛矣。舱底方言水云。并东冈之崎以左。抵桃花谷口。爱溪水清涟不能去。皆下马。各据一白石。使君瞻鼓琴。琴声益清远。瞻曰余之工乎哉。殆有假而清乎。余曰夫孰非假哉。水之洁石之假。琴又假水而清。子假手而吾假耳尔。酒一行乃起。石磴益高下。先后人相桔槔以进。至下方。板楼崩。不受人。有二槐树临流送清飙为肃客者。自此弃马而舆。径趋上方。人愈高径愈硗。往往崖落不受趾。又弃舆取山僧麻屩。任藤条猿捷盘绕者未穷。而反以睇则上方出其右。盖犹攀乔木而窥鹊巢焉。上方之阴。为铁壁数十丈。厥袤百步。壁之髻。穹窿为猛兽而攫者。掠甍焉有泉。食其趾三。直东台曰东泉。直西台曰西泉。僧言泉水得秋风则幻色为薇花黄云。中焉曰中泉。东台以古柏胜。罗衲子之植也。鹳鹤之飞。腰焉而不肩。盖其崇不可以丈。西台以江色胜。夫凭高皆江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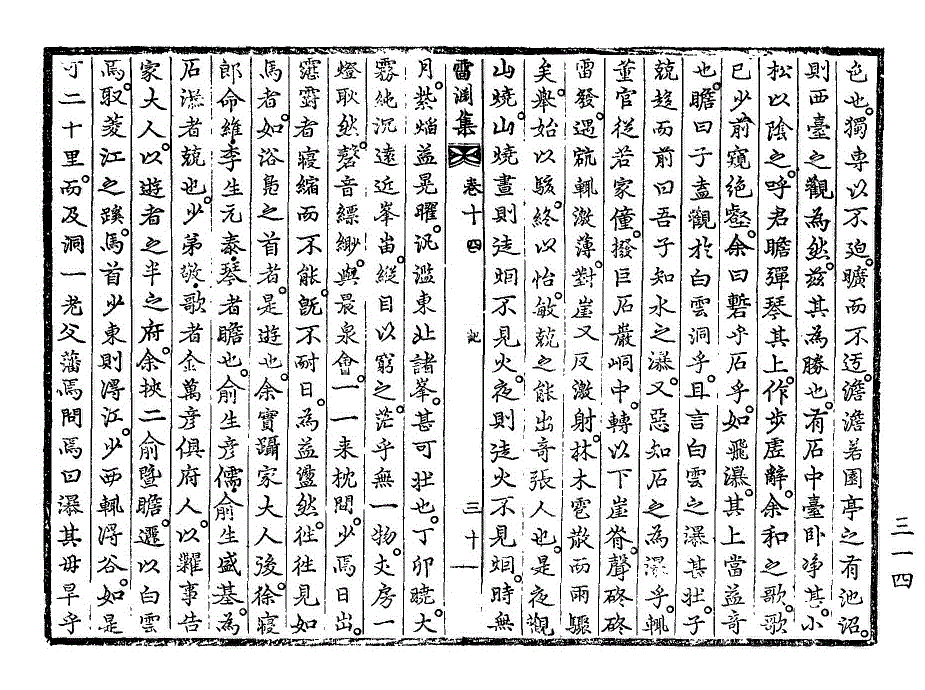 色也。独专以不迫。旷而不迂。澹澹若园亭之有池沼。则西台之观为然。玆其为胜也。有石中台卧净甚。小松以阴之。呼君瞻弹琴其上。作步虚辞。余和之歌。歌已少前窥绝壑。余曰巉乎石乎。如飞瀑。其上当益奇也。瞻曰子盍观于白云洞乎。且言白云之瀑甚壮。子兢趍而前曰吾子知水之瀑。又恶知石之为瀑乎。辄董官从若家僮。拨巨石岩峒中。转以下崖脊。声䂢䂢雷发。遇𥒳辄激薄。对崖又反激射。林木雹散而雨骤矣。举始以骇。终以怡。敏兢之能出奇张人也。是夜观山烧。山烧昼则徒烟不见火。夜则徒火不见烟。时无月。紫焰益晃曜。汎滥东北诸峰。甚可壮也。丁卯晓。大雾纯沉远近峰岫。纵目以穷之。茫乎无一物。丈房一灯耿然。磬音缥缈。与晨泉会。一一来枕间。少焉日出。霮䨴者寝缩而不能。既不耐日。为益荡然。往往见如马者。如浴凫之首者。是游也。余实蹑家大人后。徐寝郎命维,李生元泰,琴者瞻也。俞生彦儒,俞生盛基。为石瀑者兢也。少弟敬,歌者金万彦俱府人。以粜事告家大人。以游者之半之府。余挟二俞暨瞻。逦以白云焉。取菱江之蹊。马首少东则得江。少西辄得谷。如是可二十里。而及洞一老父藩焉问焉曰瀑其毋旱乎
色也。独专以不迫。旷而不迂。澹澹若园亭之有池沼。则西台之观为然。玆其为胜也。有石中台卧净甚。小松以阴之。呼君瞻弹琴其上。作步虚辞。余和之歌。歌已少前窥绝壑。余曰巉乎石乎。如飞瀑。其上当益奇也。瞻曰子盍观于白云洞乎。且言白云之瀑甚壮。子兢趍而前曰吾子知水之瀑。又恶知石之为瀑乎。辄董官从若家僮。拨巨石岩峒中。转以下崖脊。声䂢䂢雷发。遇𥒳辄激薄。对崖又反激射。林木雹散而雨骤矣。举始以骇。终以怡。敏兢之能出奇张人也。是夜观山烧。山烧昼则徒烟不见火。夜则徒火不见烟。时无月。紫焰益晃曜。汎滥东北诸峰。甚可壮也。丁卯晓。大雾纯沉远近峰岫。纵目以穷之。茫乎无一物。丈房一灯耿然。磬音缥缈。与晨泉会。一一来枕间。少焉日出。霮䨴者寝缩而不能。既不耐日。为益荡然。往往见如马者。如浴凫之首者。是游也。余实蹑家大人后。徐寝郎命维,李生元泰,琴者瞻也。俞生彦儒,俞生盛基。为石瀑者兢也。少弟敬,歌者金万彦俱府人。以粜事告家大人。以游者之半之府。余挟二俞暨瞻。逦以白云焉。取菱江之蹊。马首少东则得江。少西辄得谷。如是可二十里。而及洞一老父藩焉问焉曰瀑其毋旱乎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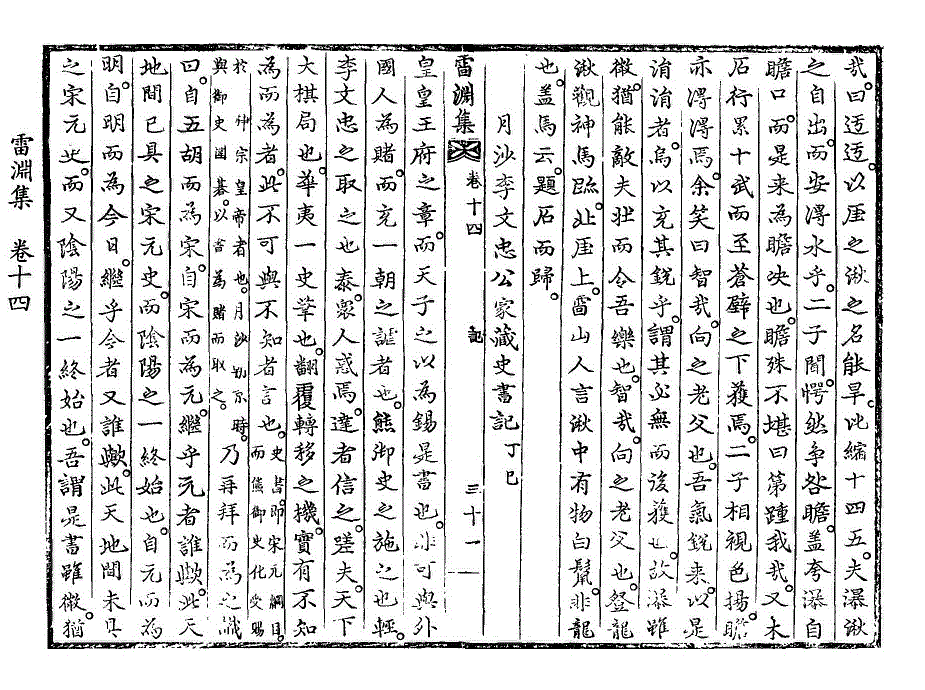 哉。曰迂迂。以厓之湫之名能旱。比缩十四五。夫瀑湫之自出。而安得水乎。二子闻。愕然争咎瞻。盖夸瀑自瞻口。而是来为瞻决也。瞻殊不堪曰第踵我哉。又木石行累十武而至苍壁之下获焉。二子相视色扬。瞻亦得得焉。余笑曰智哉。向之老父也。吾气锐来。以是涓涓者。乌以充其锐乎。谓其必无而后获也。故瀑虽微。犹能敌夫壮而令吾乐也。智哉。向之老父也。登龙湫观神马迹。北厓上。䨓山人言湫中有物白鬣。非龙也。盖马云。题石而归。
哉。曰迂迂。以厓之湫之名能旱。比缩十四五。夫瀑湫之自出。而安得水乎。二子闻。愕然争咎瞻。盖夸瀑自瞻口。而是来为瞻决也。瞻殊不堪曰第踵我哉。又木石行累十武而至苍壁之下获焉。二子相视色扬。瞻亦得得焉。余笑曰智哉。向之老父也。吾气锐来。以是涓涓者。乌以充其锐乎。谓其必无而后获也。故瀑虽微。犹能敌夫壮而令吾乐也。智哉。向之老父也。登龙湫观神马迹。北厓上。䨓山人言湫中有物白鬣。非龙也。盖马云。题石而归。月沙李文忠公家藏史书记(丁巳)
皇皇王府之章。而天子之以为锡是书也。非可与外国人为赌。而充一朝之谑者也。熊御史之施之也轻。李文忠之取之也泰。众人惑焉。达者信之。嗟夫。天下大棋局也。华夷一史笔也。翻覆转移之机。实有不知为而为者。此不可与不知者言也。(史书。即宋元纲目。而熊御史化受赐于 神宗皇帝者也。月沙朝京时。与御史围棋。以书为赌而取之。)乃再拜而为之识曰。自五胡而为宋。自宋而为元。继乎元者谁欤。此天地间已具之宋元史。而阴阳之一终始也。自元而为明。自明而为今日。继乎今者又谁欤。此天地间未具之宋元史。而又阴阳之一终始也。吾谓是书虽微。犹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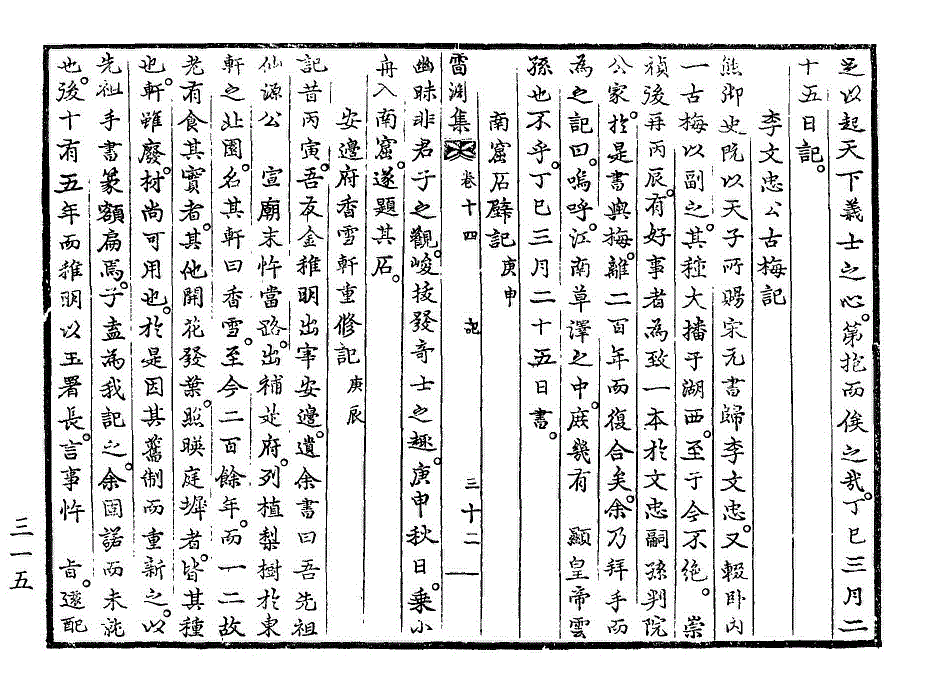 足以起天下义士之心。第抱而俟之哉。丁巳三月二十五日记。
足以起天下义士之心。第抱而俟之哉。丁巳三月二十五日记。李文忠公古梅记
熊御史既以天子所赐宋元书归李文忠。又辍卧内一古梅以副之。其种大播于湖西。至于今不绝。 崇祯后再丙辰。有好事者为致一本于文忠嗣孙判院公家。于是书与梅。离二百年而复合矣。余乃拜手而为之记曰。呜呼。江南草泽之中。庶几有 显皇帝云孙也不乎。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书。
南窟石壁记(庚申)
幽昧非君子之观。峻拔发奇士之趣。庚申秋日。乘小舟入南窟。遂题其石。
安边府香雪轩重修记(庚辰)
记昔丙寅。吾友金稚明出宰安边。遗余书曰吾先祖仙源公 宣庙末忤当路。出补是府。列植梨树于东轩之北园。名其轩曰香雪。至今二百馀年。而一二故老有食其实者。其他开花发叶。照映庭墀者。皆其种也。轩虽废。材尚可用也。于是因其旧制而重新之。以先祖手书篆额扁焉。子盍为我记之。余固诺而未就也。后十有五年而稚明以玉署长。言事忤 旨。远配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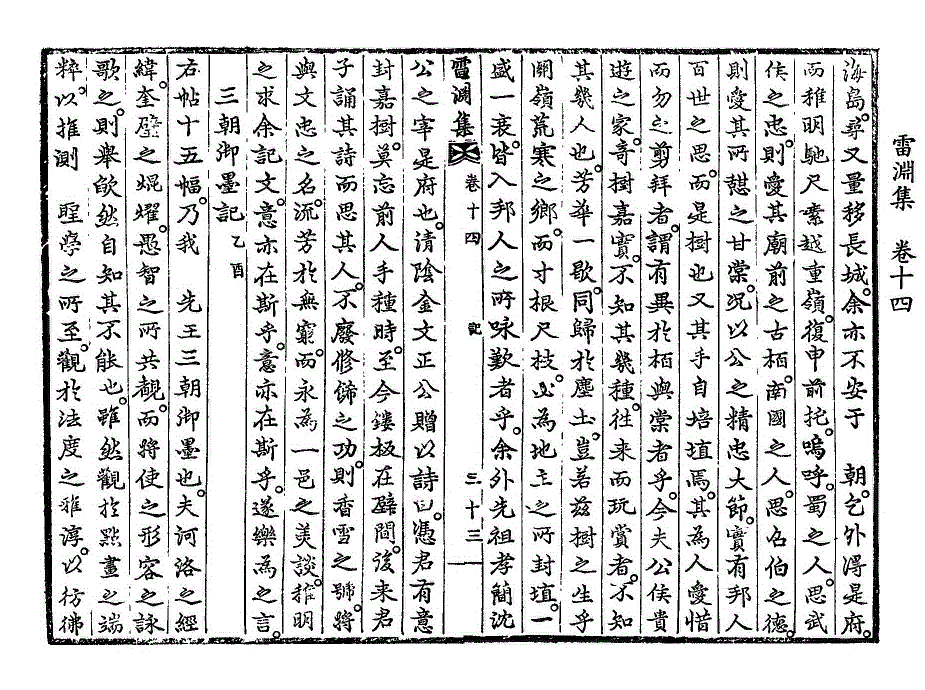 海岛。寻又量移长城。余亦不安于 朝。乞外得是府。而稚明驰尺素越重岭。复申前托。呜呼。蜀之人。思武侯之忠。则爱其庙前之古柏。南国之人。思召伯之德。则爱其所憩之甘棠。况以公之精忠大节。实有邦人百世之思。而是树也又其手自培埴焉。其为人爱惜而勿之剪拜者。谓有异于柏与棠者乎。今夫公侯贵游之家。奇树嘉实。不知其几种。往来而玩赏者。不知其几人也。芳华一歇。同归于尘土。岂若玆树之生乎关岭荒寒之乡。而寸根尺枝。必为地主之所封埴。一盛一衰。皆入邦人之所咏叹者乎。余外先祖孝简沈公之宰是府也。清阴金文正公赠以诗曰。凭君有意封嘉树。莫忘前人手种时。至今镂板在壁间。后来君子诵其诗而思其人。不废修饰之功。则香雪之号。将与文忠之名。流芳于无穷。而永为一邑之美谈。稚明之求余记文。意亦在斯乎。意亦在斯乎。遂乐为之言。
海岛。寻又量移长城。余亦不安于 朝。乞外得是府。而稚明驰尺素越重岭。复申前托。呜呼。蜀之人。思武侯之忠。则爱其庙前之古柏。南国之人。思召伯之德。则爱其所憩之甘棠。况以公之精忠大节。实有邦人百世之思。而是树也又其手自培埴焉。其为人爱惜而勿之剪拜者。谓有异于柏与棠者乎。今夫公侯贵游之家。奇树嘉实。不知其几种。往来而玩赏者。不知其几人也。芳华一歇。同归于尘土。岂若玆树之生乎关岭荒寒之乡。而寸根尺枝。必为地主之所封埴。一盛一衰。皆入邦人之所咏叹者乎。余外先祖孝简沈公之宰是府也。清阴金文正公赠以诗曰。凭君有意封嘉树。莫忘前人手种时。至今镂板在壁间。后来君子诵其诗而思其人。不废修饰之功。则香雪之号。将与文忠之名。流芳于无穷。而永为一邑之美谈。稚明之求余记文。意亦在斯乎。意亦在斯乎。遂乐为之言。三朝御墨记(乙酉)
右帖十五幅。乃我 先王三朝御墨也。夫河洛之经纬。奎璧之焜耀。愚智之所共睹。而将使之形容之咏歌之。则举欿然自知其不能也。虽然观于点画之端粹。以推测 圣学之所至。观于法度之雅淳。以彷佛
䨓渊集卷之十四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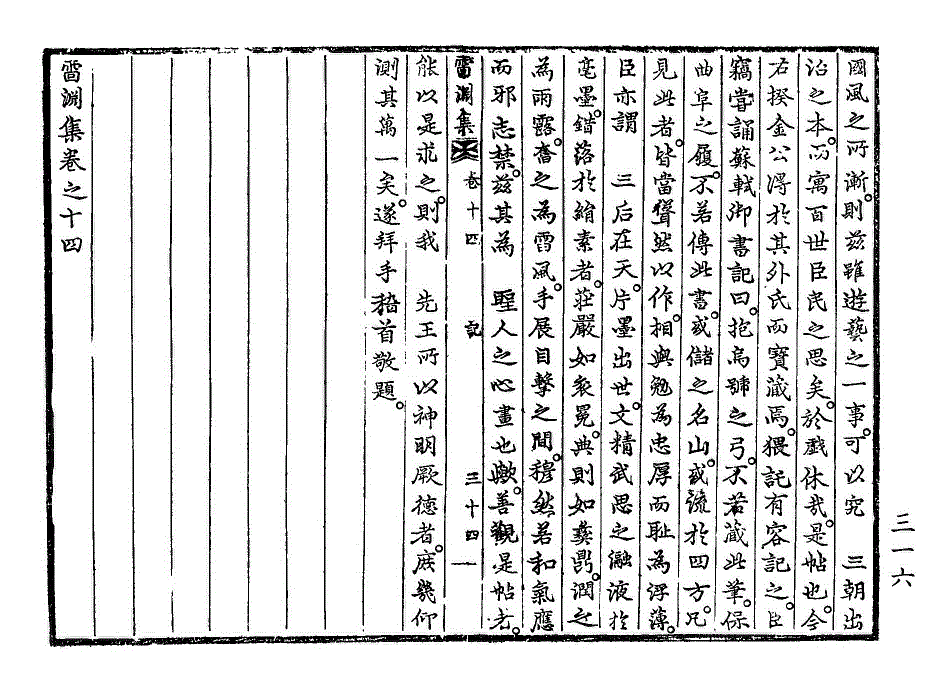 国风之所渐。则玆虽游艺之一事。可以究 三朝出治之本。而寓百世臣民之思矣。于戏休哉。是帖也。今右揆金公得于其外氏而宝藏焉。猥托有容记之。臣窃尝诵苏轼御书记曰。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或储之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以作。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臣亦谓 三后在天。片墨出世。文精武思之瀜液于毫墨。错落于绢素者。庄严如衮冕。典则如彝鼎。润之为雨露。奋之为雷风。手展目击之间。穆然若和气应而邪志禁。玆其为 圣人之心画也欤。善观是帖者。能以是求之。则我 先王所以神明厥德者。庶几仰测其万一矣。遂拜手稽首敬题。
国风之所渐。则玆虽游艺之一事。可以究 三朝出治之本。而寓百世臣民之思矣。于戏休哉。是帖也。今右揆金公得于其外氏而宝藏焉。猥托有容记之。臣窃尝诵苏轼御书记曰。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或储之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以作。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臣亦谓 三后在天。片墨出世。文精武思之瀜液于毫墨。错落于绢素者。庄严如衮冕。典则如彝鼎。润之为雨露。奋之为雷风。手展目击之间。穆然若和气应而邪志禁。玆其为 圣人之心画也欤。善观是帖者。能以是求之。则我 先王所以神明厥德者。庶几仰测其万一矣。遂拜手稽首敬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