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x 页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杂著
杂著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3H 页
 史评[上]
史评[上]文王拘羑里。以散宜生之赂而免云。诬圣贤乱君臣。启万世幽阴之径者。此说俑之也。纣虽暴虐。天命未绝。则文王之君也。为人臣子者。以美女珠玉。蛊惑其君。即乱臣贼子之事。而谓文王为之乎。或曰。宜生自为之。文王何与焉。曰。人臣无心。以君为心。大盭于文王之心而宜生行之。是贰于文王。而陷文王于不义也。文王一日脱于羑里。顾不行讨于宜生哉。宜生贤者。岂有是哉。然此特据君臣之义而言尔。设使纣非天王。文非臣子。世岂有行赂图生之圣人乎。曹伯失国。其竖侯孺。货晋之筮史。适文公有疾。以曹为解。文公遂复曹伯。春秋大书曹伯襄归于曹。罪其以赂得国而特名之。比于失地灭同姓之君。圣人严于义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者如此。呜呼。文王之命在天。独夫纣。焉能杀文王。而散氏之子。焉能使文王不死哉。余特书此。以戒夫后世之藉口圣贤。以开幽阴之径者。
书吴子使札来。以不称公子。又不书字。故胡文定以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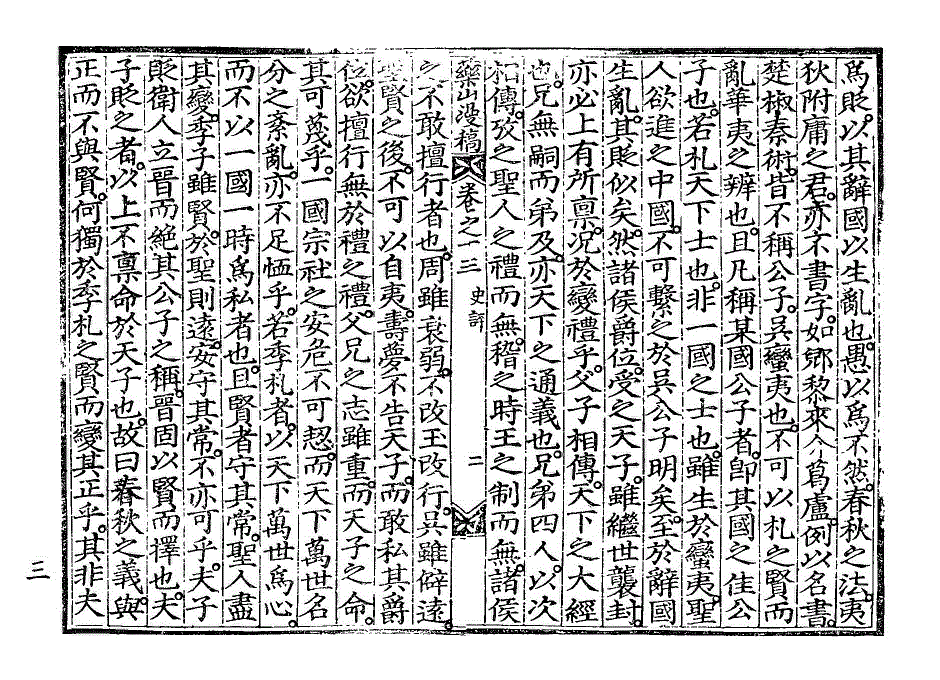 为贬。以其辞国以生乱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法。夷狄附庸之君。亦不书字。如郳黎来介葛卢。例以名书。楚椒,秦术。皆不称公子。吴蛮夷也。不可以札之贤而乱华夷之辨也。且凡称某国公子者。即其国之佳公子也。若札天下士也。非一国之士也。虽生于蛮夷。圣人欲进之中国。不可系之于吴公子明矣。至于辞国生乱。其贬似矣。然诸侯爵位。受之天子。虽继世袭封。亦必上有所禀。况于变礼乎。父子相传。天下之大经也。兄无嗣而弟及。亦天下之通义也。兄弟四人。以次相传。考之圣人之礼而无。稽之时王之制而无。诸侯之不敢擅行者也。周虽衰弱。不改玉改行。吴虽僻远。圣贤之后。不可以自夷。寿梦不告天子。而敢私其爵位。欲擅行无于礼之礼。父兄之志虽重。而天子之命。其可蔑乎。一国宗社之安危不可恝。而天下万世名分之紊乱。亦不足恤乎。若季札者。以天下万世为心。而不以一国一时为私者也。且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季子虽贤。于圣则远。安守其常。不亦可乎。夫子贬卫人立晋而绝其公子之称。晋固以贤而择也。夫子贬之者。以上不禀命于天子也。故曰春秋之义。与正而不与贤。何独于季札之贤而变其正乎。其非夫
为贬。以其辞国以生乱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法。夷狄附庸之君。亦不书字。如郳黎来介葛卢。例以名书。楚椒,秦术。皆不称公子。吴蛮夷也。不可以札之贤而乱华夷之辨也。且凡称某国公子者。即其国之佳公子也。若札天下士也。非一国之士也。虽生于蛮夷。圣人欲进之中国。不可系之于吴公子明矣。至于辞国生乱。其贬似矣。然诸侯爵位。受之天子。虽继世袭封。亦必上有所禀。况于变礼乎。父子相传。天下之大经也。兄无嗣而弟及。亦天下之通义也。兄弟四人。以次相传。考之圣人之礼而无。稽之时王之制而无。诸侯之不敢擅行者也。周虽衰弱。不改玉改行。吴虽僻远。圣贤之后。不可以自夷。寿梦不告天子。而敢私其爵位。欲擅行无于礼之礼。父兄之志虽重。而天子之命。其可蔑乎。一国宗社之安危不可恝。而天下万世名分之紊乱。亦不足恤乎。若季札者。以天下万世为心。而不以一国一时为私者也。且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季子虽贤。于圣则远。安守其常。不亦可乎。夫子贬卫人立晋而绝其公子之称。晋固以贤而择也。夫子贬之者。以上不禀命于天子也。故曰春秋之义。与正而不与贤。何独于季札之贤而变其正乎。其非夫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4H 页
 子之意明矣。春秋之笔。未必字字有义。书吴子使札来。纪事而已。非寓褒贬也。夫子善季札。故公,谷傅会以为褒。胡文定过求以为贬。朱子论季札让国曰。可以受。可以无受。朱子以受为害义者也。
子之意明矣。春秋之笔。未必字字有义。书吴子使札来。纪事而已。非寓褒贬也。夫子善季札。故公,谷傅会以为褒。胡文定过求以为贬。朱子论季札让国曰。可以受。可以无受。朱子以受为害义者也。以女而不妇。妄论宋伯姬者。不过看死生为大事尔。自伯姬视之。焚死事小。害贞事大。左氏乌能知伯姬哉。端坐烈焰中。人皆壮之。而若伯姬见其礼。不见火燄。处之寻常尔。呜呼。闻伯姬之风者。懒妇立。呜呼。伯姬其百世之女师乎。
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世俗以廉与立。看作伯夷气像。故每失伯夷。辄想像为激切皎厉之人。是岂足与论伯夷哉。顽故廉。懦故立。彼闻风而兴起者。握拳竖发。不得不然尔。若伯夷安闲宽广。曷尝一毫费气力。恭伯姬亦然。世人看伯姬作烈。伯姬幽闲静传而已。曷尝有烈意思。闻伯姬而兴起者。方为烈尔。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丈夫在世。不可须臾忘此意。其正大之气。撑于肠脰。充于四体。养之既久。则自至于伯夷安闲之域也。孟子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或曰。奋者非激厉气象乎。曰非也。奋者作兴之谓。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4L 页
 孟子之言。专指兴起百世而言。如周王作人云尔。亦不属伯夷气像。
孟子之言。专指兴起百世而言。如周王作人云尔。亦不属伯夷气像。纪季以酅入于齐。诸儒皆以为纪季知齐之必灭纪。先以酅事齐。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故春秋贤之云。非也。忧纪之将亡。而纳土以存社稷可也。知纪之必亡。而析地以附雠邦。不可也。季之入齐。欲存纪也。明知死疾之不可医。而为子弟者。皇皇祷祀。聊以尽吾心焉耳。纪虽将亡。一日之命未绝。而先自贰。请后五庙。是非臣子之所敢出也。齐视耽耽。不灭不已。事之以土地而不得免。事之以臣妾而不得免。于是乎纪侯大去其国。齐既并纪。其欲果矣。遂舍酅不绝其祀。以艳观听。此非季初望也。后人按其迹而傅会谓季先自判误矣。纪季者有种蠡之心而无其才。纪侯者类太王之迹而无其仁者也。有以季比微子者。尤不可。曷尝有殷未亡而抱器诣周之微子。况齐非武王之天吏乎。
公羊传曰。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襄公为此。事祖祢之心尽矣。胡传以为仲尼书柯之盟。其辞无贬。则公羊谓复九世之雠。春秋贤之者妄矣。特借襄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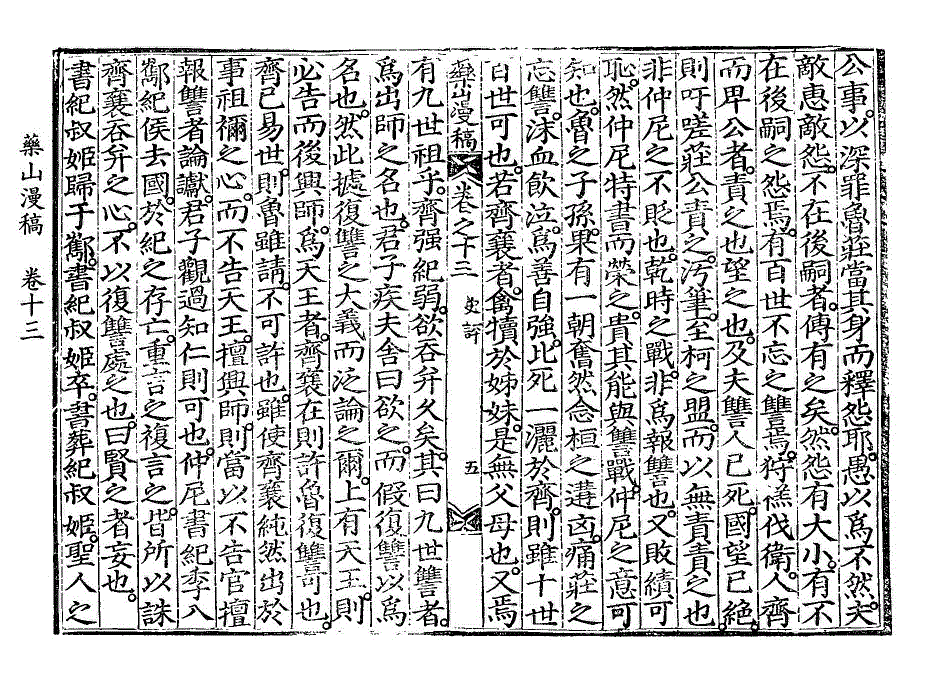 公事。以深罪鲁庄当其身而释怨耶。愚以为不然。夫敌惠敌怨。不在后嗣者。传有之矣。然怨有大小。有不在后嗣之怨焉。有百世不忘之雠焉。狩禚伐卫。人齐而卑公者。责之也望之也。及夫雠人已死。国望已绝。则吁嗟庄公责之。污笔。至柯之盟。而以无责责之也。非仲尼之不贬也。乾时之战。非为报雠也。又败绩可耻。然仲尼特书而荣之。贵其能与雠战。仲尼之意可知也。鲁之子孙。果有一朝奋然念桓之遘凶。痛庄之忘雠。沫血饮泣。为善自强。比死一洒于齐。则虽十世百世可也。若齐襄者。禽犊于姊妹。是无父母也。又焉有九世祖乎。齐强纪弱。欲吞并久矣。其曰九世雠者。为出师之名也。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假复雠以为名也。然此据复雠之大义而泛论之尔。上有天王。则必告而后兴师。为天王者。齐襄在则许鲁复雠可也。齐已易世。则鲁虽请。不可许也。虽使齐襄纯然出于事祖祢之心。而不告天王。擅兴师。则当以不告官擅报雠者论谳。君子观过知仁则可也。仲尼书纪季入酅纪侯去国。于纪之存亡。重言之复言之。皆所以诛齐襄吞并之心。不以复雠处之也。曰贤之者妄也。
公事。以深罪鲁庄当其身而释怨耶。愚以为不然。夫敌惠敌怨。不在后嗣者。传有之矣。然怨有大小。有不在后嗣之怨焉。有百世不忘之雠焉。狩禚伐卫。人齐而卑公者。责之也望之也。及夫雠人已死。国望已绝。则吁嗟庄公责之。污笔。至柯之盟。而以无责责之也。非仲尼之不贬也。乾时之战。非为报雠也。又败绩可耻。然仲尼特书而荣之。贵其能与雠战。仲尼之意可知也。鲁之子孙。果有一朝奋然念桓之遘凶。痛庄之忘雠。沫血饮泣。为善自强。比死一洒于齐。则虽十世百世可也。若齐襄者。禽犊于姊妹。是无父母也。又焉有九世祖乎。齐强纪弱。欲吞并久矣。其曰九世雠者。为出师之名也。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假复雠以为名也。然此据复雠之大义而泛论之尔。上有天王。则必告而后兴师。为天王者。齐襄在则许鲁复雠可也。齐已易世。则鲁虽请。不可许也。虽使齐襄纯然出于事祖祢之心。而不告天王。擅兴师。则当以不告官擅报雠者论谳。君子观过知仁则可也。仲尼书纪季入酅纪侯去国。于纪之存亡。重言之复言之。皆所以诛齐襄吞并之心。不以复雠处之也。曰贤之者妄也。书纪叔姬归于酅。书纪叔姬卒。书葬纪叔姬。圣人之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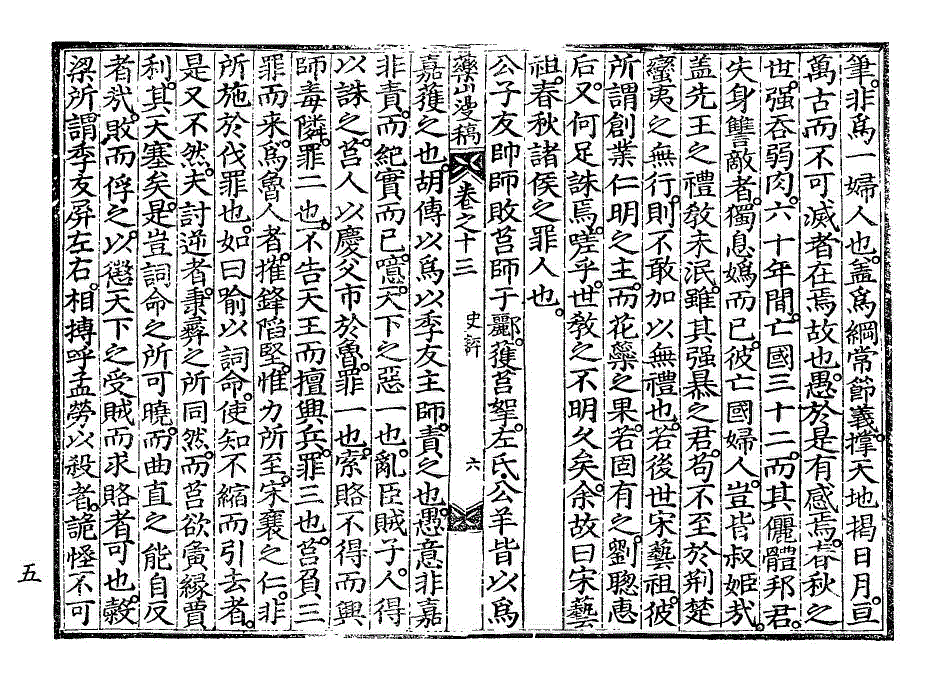 笔。非为一妇人也。盖为纲常节义。撑天地揭日月。亘万古而不可灭者在焉故也。愚于是有感焉。春秋之世。强吞弱肉。六十年间。亡国三十二。而其俪体邦君。失身雠敌者。独息妫而已。彼亡国妇人。岂皆叔姬哉。盖先王之礼教未泯。虽其强暴之君。苟不至于荆楚蛮夷之无行。则不敢加以无礼也。若后世宋艺祖。彼所谓创业仁明之主。而花蕊之果。若固有之。刘聪惠后。又何足诛焉。嗟乎。世教之不明久矣。余故曰宋艺祖。春秋诸侯之罪人也。
笔。非为一妇人也。盖为纲常节义。撑天地揭日月。亘万古而不可灭者在焉故也。愚于是有感焉。春秋之世。强吞弱肉。六十年间。亡国三十二。而其俪体邦君。失身雠敌者。独息妫而已。彼亡国妇人。岂皆叔姬哉。盖先王之礼教未泯。虽其强暴之君。苟不至于荆楚蛮夷之无行。则不敢加以无礼也。若后世宋艺祖。彼所谓创业仁明之主。而花蕊之果。若固有之。刘聪惠后。又何足诛焉。嗟乎。世教之不明久矣。余故曰宋艺祖。春秋诸侯之罪人也。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挐。左氏,公羊皆以为嘉获之也。胡传以为以季友主师。责之也。愚意非嘉非责。而纪实而已。噫。天下之恶一也。乱臣贼子。人得以诛之。莒人以庆父市于鲁。罪一也。索赂不得而兴师毒邻。罪二也。不告天王而擅兴兵。罪三也。莒负三罪而来。为鲁人者。摧锋陷坚。惟力所至。宋襄之仁。非所施于伐罪也。如曰喻以词命。使知不缩而引去者。是又不然。夫讨逆者。秉彝之所同然。而莒欲夤缘贾利。其天塞矣。是岂词命之所可晓。而曲直之能自反者哉。败而俘之。以惩天下之受贼而求赂者可也。谷梁所谓季友屏左右。相搏呼孟劳以杀者。诡怪不可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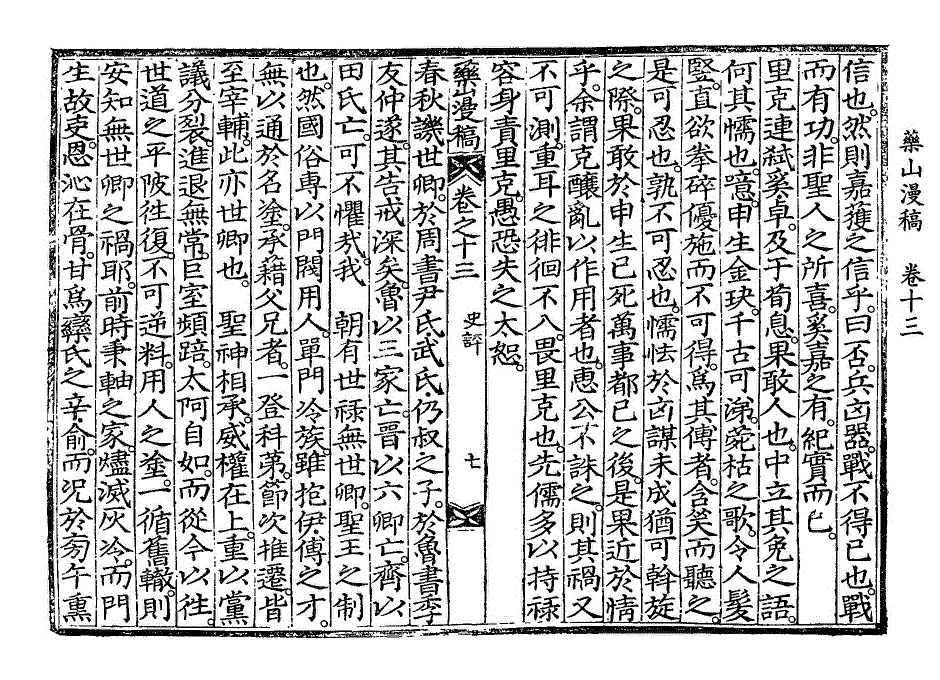 信也。然则嘉获之信乎。曰否。兵凶器。战不得已也。战而有功。非圣人之所喜。奚嘉之有。纪实而已。
信也。然则嘉获之信乎。曰否。兵凶器。战不得已也。战而有功。非圣人之所喜。奚嘉之有。纪实而已。里克连弑奚,卓。及于荀息。果敢人也。中立其免之语。何其懦也。噫。申生金玦。千古可涕。菀枯之歌。令人发竖。直欲拳碎优施而不可得。为其傅者。含笑而听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懦怯于凶谋未成犹可斡旋之际。果敢于申生已死万事都已之后。是果近于情乎。余谓克酿乱以作用者也。惠公不诛之。则其祸又不可测。重耳之徘徊不入。畏里克也。先儒多以持禄容身责里克。愚恐失之太恕。
春秋讥世卿。于周书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鲁书季友,仲遂。其告戒深矣。鲁以三家亡。晋以六卿亡。齐以田氏亡。可不惧哉。我 朝有世禄无世卿。圣王之制也。然国俗专以门阀用人。单门冷族。虽抱伊,傅之才。无以通于名涂。承藉父兄者。一登科第。节次推迁。皆至宰辅。此亦世卿也。 圣神相承。威权在上。重以党议分裂。进退无常。巨室频踣。太阿自如。而从今以往。世道之平陂往复。不可逆料。用人之涂。一循旧辙。则安知无世卿之祸耶。前时秉轴之家。烬灭灰冷。而门生故吏。恩沁在骨。甘为栾氏之辛,俞。而况于旁午熏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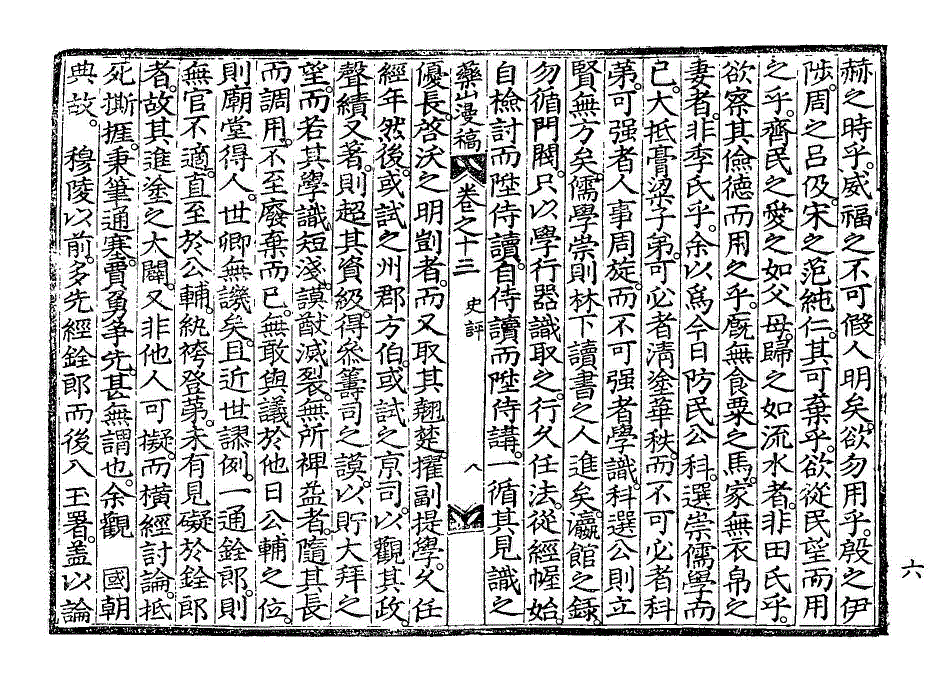 赫之时乎。威福之不可假人明矣。欲勿用乎。殷之伊陟。周之吕伋。宋之范纯仁。其可弃乎。欲从民望而用之乎。齐民之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者。非田氏乎。欲察其俭德而用之乎。厩无食粟之马。家无衣帛之妻者。非季氏乎。余以为今日防民公科。选崇儒学而已。大抵膏粱子弟。可必者清涂华秩。而不可必者科第。可强者人事周旋。而不可强者学识。科选公则立贤无方矣。儒学崇则林下读书之人进矣。瀛馆之录。勿循门阀。只以学行器识取之。行久任法。从经幄始。自检讨而升侍读。自侍读而升侍讲。一循其见识之优长。启沃之明剀者。而又取其翘楚。擢副提学。久任经年然后。或试之州郡方伯。或试之京司。以观其政。声绩又著。则超其资级。得参筹司之谟。以贮大拜之望。而若其学识短浅。谟猷灭裂。无所裨益者。随其长而调用。不至废弃而已。无敢与议于他日公辅之位。则庙堂得人。世卿无讥矣。且近世谬例。一通铨郎。则无官不适。直至于公辅。纨裤登第。未有见碍于铨郎者。故其进涂之大辟。又非他人可拟。而横经讨论。抵死撕挨。秉笔通塞。贾勇争先。甚无谓也。余观 国朝典故。 穆陵以前。多先经铨郎而后入玉署。盖以论
赫之时乎。威福之不可假人明矣。欲勿用乎。殷之伊陟。周之吕伋。宋之范纯仁。其可弃乎。欲从民望而用之乎。齐民之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者。非田氏乎。欲察其俭德而用之乎。厩无食粟之马。家无衣帛之妻者。非季氏乎。余以为今日防民公科。选崇儒学而已。大抵膏粱子弟。可必者清涂华秩。而不可必者科第。可强者人事周旋。而不可强者学识。科选公则立贤无方矣。儒学崇则林下读书之人进矣。瀛馆之录。勿循门阀。只以学行器识取之。行久任法。从经幄始。自检讨而升侍读。自侍读而升侍讲。一循其见识之优长。启沃之明剀者。而又取其翘楚。擢副提学。久任经年然后。或试之州郡方伯。或试之京司。以观其政。声绩又著。则超其资级。得参筹司之谟。以贮大拜之望。而若其学识短浅。谟猷灭裂。无所裨益者。随其长而调用。不至废弃而已。无敢与议于他日公辅之位。则庙堂得人。世卿无讥矣。且近世谬例。一通铨郎。则无官不适。直至于公辅。纨裤登第。未有见碍于铨郎者。故其进涂之大辟。又非他人可拟。而横经讨论。抵死撕挨。秉笔通塞。贾勇争先。甚无谓也。余观 国朝典故。 穆陵以前。多先经铨郎而后入玉署。盖以论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7H 页
 思为重故也。今亦以三司通拟铨郎。使其地望出于玉署之下。以绝新进趍利之涂。则庶乎其可也。或曰。世有不学而为名公卿者。子言不几隘乎。曰。自古名臣硕辅。皆读书人。不学而忠者。霍光一人。而亦胎汉室之祸。宁失一霍光。不可启三家六卿之祸也。
思为重故也。今亦以三司通拟铨郎。使其地望出于玉署之下。以绝新进趍利之涂。则庶乎其可也。或曰。世有不学而为名公卿者。子言不几隘乎。曰。自古名臣硕辅。皆读书人。不学而忠者。霍光一人。而亦胎汉室之祸。宁失一霍光。不可启三家六卿之祸也。汉宣明主也。权纲在手。许史庸庸。非窃威福者。然王氏专擅。实基于此。人主贻燕。可不谋之于始。防之于微。而为戚里者。亦可以履冰矣。
书郑人来输平。贬也。鲁,郑有旧怨。一矢相加遗久矣。一朝解怨释仇。同归于好。宜圣人之所善也。奚以贬乎。输者纳也。平者成也。来输者。必有挟而以利相结也。圣人之贬。非贬脩睦也。贬其利心也。党论分裂。仇怨日深。消融保合。以藩王室。岂非天下之至善。而万一以功名富贵之念参错于其间。即春秋之输平也。士大夫所当反求于心术之微而不可忽者也。嗟乎。利之祸人国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亲。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诸侯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则而国危矣。
春秋书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曰。其称弟何。母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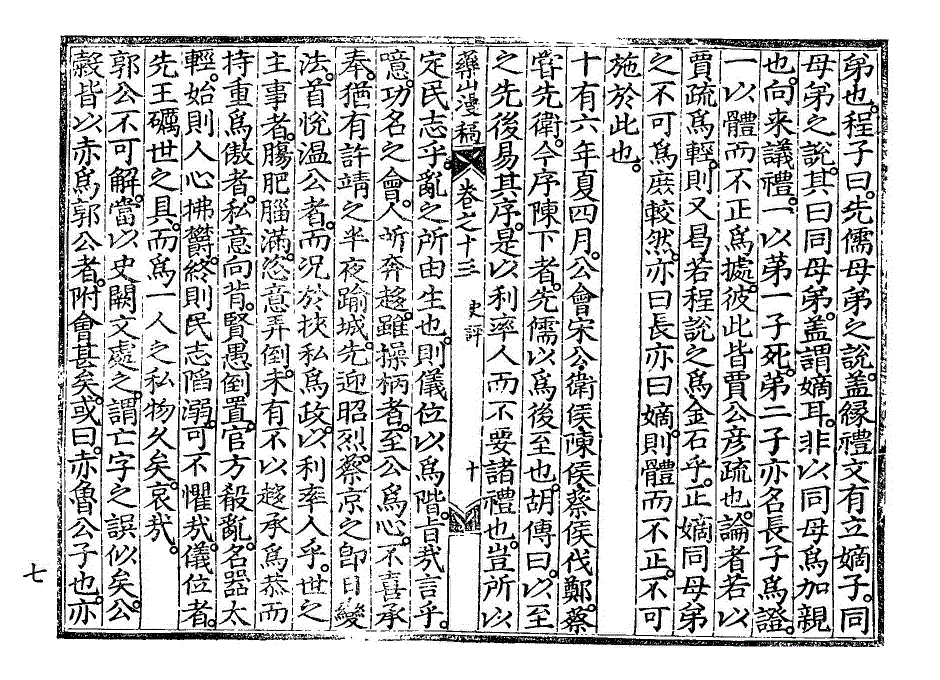 弟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说。盖缘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为加亲也。向来议礼。一以第一子死。第二子亦名长子为證。一以体而不正为据。彼此皆贾公彦疏也。论者若以贾疏为轻。则又曷若程说之为金石乎。正嫡同母弟之不可为庶较然。亦曰长亦曰嫡。则体而不正。不可施于此也。
弟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说。盖缘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为加亲也。向来议礼。一以第一子死。第二子亦名长子为證。一以体而不正为据。彼此皆贾公彦疏也。论者若以贾疏为轻。则又曷若程说之为金石乎。正嫡同母弟之不可为庶较然。亦曰长亦曰嫡。则体而不正。不可施于此也。十有六年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蔡尝先卫。今序陈下者。先儒以为后至也。胡传曰。以至之先后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诸礼也。岂所以定民志乎。乱之所由生也。则仪位以为阶。旨哉言乎。噫。功名之会。人所奔趍。虽操柄者。至公为心。不喜承奉。犹有许靖之半夜踰城。先迎昭烈。蔡京之即日变法。首悦温公者。而况于挟私为政。以利率人乎。世之主事者。肠肥脑满。恣意弄倒。未有不以趍承为恭而持重为傲者。私意向背。贤愚倒置。官方殽乱。名器太轻。始则人心拂郁。终则民志陷溺。可不惧哉。仪位者。先王砺世之具。而为一人之私物久矣。哀哉。
郭公不可解。当以史阙文处之。谓亡字之误似矣。公谷皆以赤为郭公者。附会甚矣。或曰。赤鲁公子也。亦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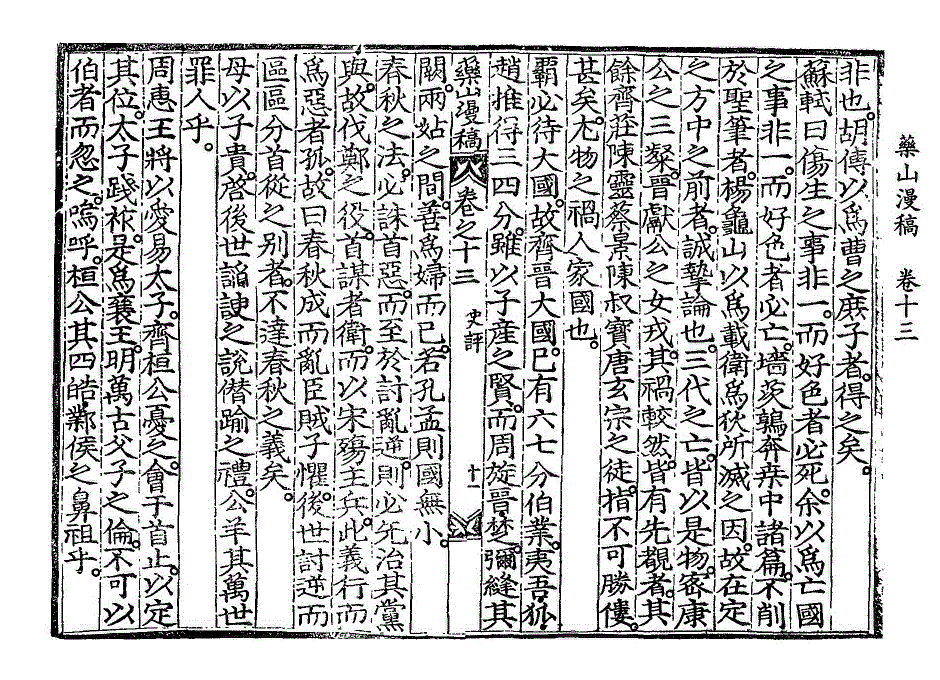 非也。胡传以为曹之庶子者。得之矣。
非也。胡传以为曹之庶子者。得之矣。苏轼曰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余以为亡国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亡。墙茨鹑奔桑中诸篇。不削于圣笔者。杨龟山以为载卫为狄所灭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者。诚挚论也。三代之亡。皆以是物。密康公之三粲。晋献公之女戎。其祸较然。皆有先睹者。其馀齐庄陈灵蔡景陈叔宝唐玄宗之徒。指不可胜偻。甚矣。尤物之祸人家国也。
霸必待大国。故齐晋大国。已有六七分伯业。夷吾,狐,赵推得三四分。虽以子产之贤。而周旋晋,楚。弥缝其阙。两姑之间。善为妇而已。若孔孟则国无小。
春秋之法。必诛首恶。而至于讨乱逆。则必先治其党与。故伐郑之役。首谋者卫。而以宋殇主兵。此义行而为恶者孤。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后世讨逆而区区分首从之别者。不达春秋之义矣。
母以子贵。启后世谄谀之说僭踰之礼。公羊其万世罪人乎。
周惠王将以爱易太子。齐桓公忧之。会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祚。是为襄王。明万古父子之伦。不可以伯者而忽之。呜呼。桓公其四皓,邺侯之鼻祖乎。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8L 页
 叔武,元咺,景泰,于谦。皆为社稷也。成公,英宗皆不念鞠子哀者也。然叔武尽其道。故成公杀之。其罪重。景泰不避位。故英宗废之。其罪轻。元咺前忠后逆。于谦大节小疵。
叔武,元咺,景泰,于谦。皆为社稷也。成公,英宗皆不念鞠子哀者也。然叔武尽其道。故成公杀之。其罪重。景泰不避位。故英宗废之。其罪轻。元咺前忠后逆。于谦大节小疵。甚矣。卫文公燬之无道也。合诸侯城楚丘。惠徼福于康叔者。非齐桓乎。文公身出灰烬之中。沐浴其赐。而一日桓公卒。忽焉忘之而伐其丧。宜不能保其子而宗社再圮也。然则秉心塞渊。诗人之赞何居。饥者易食。渴者易饮。彼承懿公昏暴之后。稍存心于勤俭。民之悦之。如大旱之甘霔耳。大布大帛。灵雨星驾。则见取于诗。伐齐灭邢。背恩迁怒。则见罪于春秋。恶而知其美。爱而知其恶。见圣人至公无适莫之心也。于此又有感焉。使齐桓之恤卫。纯然出于怵惕恻隐之心。则燬虽无道。何忍背之。彼虽厌然要誉于乡党朋友。而功利之私。虚假之念。难掩十目之视。受之者不以为德。忍于伐丧而不顾。燬虽负德。小白与有罪焉。甚矣。虚假之不能感人而功利之不见报施也。
季友岂非贤辅。田完岂非名臣。友之后未必世世皆友。而友之死。鲁国未为无友也。完之后未必世世皆完。而完之死。齐国未为无完也。齐鲁之君。不以待友,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9H 页
 完者待一国之贤者。而反使友,完之后。私友,完之位。宜其君逐于季而国移于田也。晋之巨室强盛。自穆侯至平公。乱兵不辍。祸败无已。平公恐及其身。问于阳毕。阳毕对曰。本根犹树。枝叶益长。今若大其柯。绝其本根。可以少间。图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平公于是逐栾盈之党。以国伦数而遣之。起韩,魏,赵之后而立之。是以没平公之身无内乱。阳毕之力也。然韩,魏,赵浸盛。卒移晋祚。天下其无栾氏乎。阳毕之为公谋曰抡贤人可也。何必曰贤人之后乎。平公之立贤也。敷求于四方可也。何必求之于三家乎。凡人以犬马齿保目所见。以为当然而不知变也。晋俗之慕巨室盖久矣。献惠之间。里,丕执邦命。文公以后。栾,郤,胥,原缔国柄。前车后辙头尾相㘅。而阳毕之见又如此。信乎习俗之溺人也。平公一扫弊族。处置赫然。诚能以此时得天下之贤俊。共天位共天禄。则近而数世之仁。远而百世之仁也。岂止于殁其身而已。
完者待一国之贤者。而反使友,完之后。私友,完之位。宜其君逐于季而国移于田也。晋之巨室强盛。自穆侯至平公。乱兵不辍。祸败无已。平公恐及其身。问于阳毕。阳毕对曰。本根犹树。枝叶益长。今若大其柯。绝其本根。可以少间。图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平公于是逐栾盈之党。以国伦数而遣之。起韩,魏,赵之后而立之。是以没平公之身无内乱。阳毕之力也。然韩,魏,赵浸盛。卒移晋祚。天下其无栾氏乎。阳毕之为公谋曰抡贤人可也。何必曰贤人之后乎。平公之立贤也。敷求于四方可也。何必求之于三家乎。凡人以犬马齿保目所见。以为当然而不知变也。晋俗之慕巨室盖久矣。献惠之间。里,丕执邦命。文公以后。栾,郤,胥,原缔国柄。前车后辙头尾相㘅。而阳毕之见又如此。信乎习俗之溺人也。平公一扫弊族。处置赫然。诚能以此时得天下之贤俊。共天位共天禄。则近而数世之仁。远而百世之仁也。岂止于殁其身而已。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记陨霜不杀草。何为记之也。曰。此言可杀也。夫宜杀而不杀。则李梅冬实。天失其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9L 页
 道。草木犹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时失其序。则其施必悖。无以统万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则其权必丧。无以服万民矣。盖圣人之言简。而此对甚敷衍何也。当时禄去公室。权归三桓。正陨霜宜杀之时。而简辞微意。人或不达。则其启后世人君好杀之祸者不难。故圣人之训。委曲至此。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以使民战栗。亦劝哀公之威断而去三桓张公室者也。其心未尝不善。而其旨傅会。其言急迫。未必君心之开悟。而徒成后世之厉阶。此仲尼所以有成事不说之叹也。哀公威断。当施于权奸。何关于民。去三桓则民将蹈舞之不暇。奚战栗之有。噫。宰我误矣。
道。草木犹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时失其序。则其施必悖。无以统万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则其权必丧。无以服万民矣。盖圣人之言简。而此对甚敷衍何也。当时禄去公室。权归三桓。正陨霜宜杀之时。而简辞微意。人或不达。则其启后世人君好杀之祸者不难。故圣人之训。委曲至此。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以使民战栗。亦劝哀公之威断而去三桓张公室者也。其心未尝不善。而其旨傅会。其言急迫。未必君心之开悟。而徒成后世之厉阶。此仲尼所以有成事不说之叹也。哀公威断。当施于权奸。何关于民。去三桓则民将蹈舞之不暇。奚战栗之有。噫。宰我误矣。晋襄公卒。太子幼。晋人欲立长君。逆公子雍于秦。而赵盾中变其说。御秦败之。春秋书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先蔑奔秦。噫。君臣之分。天纲截严。一有私心游移其间则逆也。灵公虽幼。国本已定。襄无贰教。民无异望。而盾乃欲纳庶孽夺正位。已不容于诛。及夫中变而御秦也。非觉其非而归于正也。特畏穆嬴之偪而改其图也。为人臣子。计较一身之祸福。而视君位如奕棋。君臣之伦斁。则中国而入于夷狄矣。宜其与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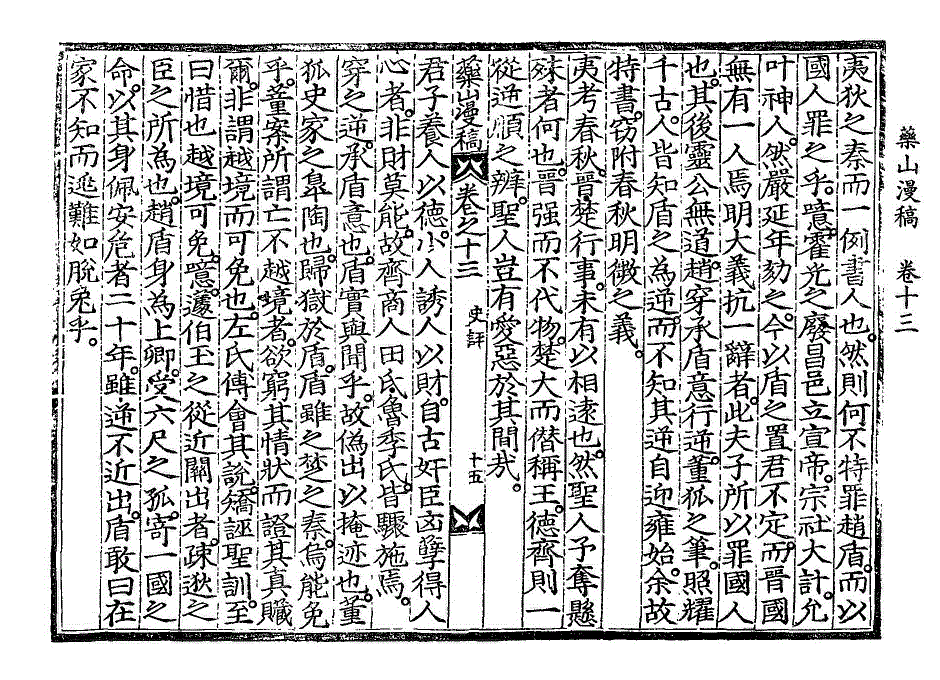 夷狄之秦而一例书人也。然则何不特罪赵盾。而以国人罪之乎。噫。霍光之废昌邑立宣帝。宗社大计。允叶神人。然严延年劾之。今以盾之置君不定。而晋国无有一人焉明大义抗一辞者。此夫子所以罪国人也。其后灵公无道。赵穿承盾意行逆。董狐之笔。照耀千古。人皆知盾之为逆。而不知其逆自迎雍始。余故特书。窃附春秋明微之义。
夷狄之秦而一例书人也。然则何不特罪赵盾。而以国人罪之乎。噫。霍光之废昌邑立宣帝。宗社大计。允叶神人。然严延年劾之。今以盾之置君不定。而晋国无有一人焉明大义抗一辞者。此夫子所以罪国人也。其后灵公无道。赵穿承盾意行逆。董狐之笔。照耀千古。人皆知盾之为逆。而不知其逆自迎雍始。余故特书。窃附春秋明微之义。夷考春秋。晋,楚行事。未有以相远也。然圣人予夺悬殊者何也。晋强而不代物。楚大而僭称王。德齐则一从逆顺之辨。圣人岂有爱恶于其间哉。
君子养人以德。小人诱人以财。自古奸臣凶孽得人心者。非财莫能。故齐商人田氏,鲁季氏。皆骤施焉。
穿之逆。承盾意也。盾实与闻乎。故伪出以掩迹也。董狐史家之皋陶也。归狱于盾。盾虽之楚之秦。乌能免乎。蕫案所谓亡不越境者。欲穷其情状而證其真赃尔。非谓越境而可免也。左氏傅会其说。矫诬圣训。至曰惜也越境可免。噫。蘧伯玉之从近关出者。疏逖之臣之所为也。赵盾身为上卿。受六尺之孤。寄一国之命。以其身佩安危者二十年。虽逆不近出。盾敢曰在家不知而逃难如脱兔乎。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0L 页
 春秋大义。讨乱贼与攘夷狄也。楚庄以蛮夷之长。能讨少西氏之逆。春秋进而书爵。岂讨贼之义。重于攘夷而然欤。夷狄之所以为夷狄者。以其无父无君也。乱臣贼子。交横于中国。而鸣讨之义。出于蛮夷。则是夷夏易位矣。书曰楚子者。乃所以伤诸夏之亡也。
春秋大义。讨乱贼与攘夷狄也。楚庄以蛮夷之长。能讨少西氏之逆。春秋进而书爵。岂讨贼之义。重于攘夷而然欤。夷狄之所以为夷狄者。以其无父无君也。乱臣贼子。交横于中国。而鸣讨之义。出于蛮夷。则是夷夏易位矣。书曰楚子者。乃所以伤诸夏之亡也。鲁之削也宜矣。什一者。三代金石之制。暴君污吏之不敢坏。而宣公初税亩。其后成公作兵甲。哀公用田赋。鲁秉周礼。诸国之所视效也。子产之丘赋。魏文之增租赋。暴秦之开阡陌更赋税。实自宣公作俑。当时如有王者作。正坏乱王制之罪。则当归狱于鲁宣矣。
夷狄豺狼。不可亲也。若非武王天吏之德八域同声。羌髳微卢不期而会者。则未有不受其祸者。周襄王以狄伐郑。唐肃宗以回纥戡乱。吴三桂以清击流贼。祸有大小而皆可鉴也。故春秋于晋以白狄伐秦。秦以白狄伐晋。皆谨书以为戒。
曹宣公卒于师。公子负刍杀太子自立。晋厉公执之。又不敢自治。归于京师。此春秋伯讨第一。
宋共公之丧。荡氏,鱼氏之徒。作乱杀公子肥。右师华元曰。我司君臣之训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国人许之讨而后入。杀荡山出鱼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1H 页
 石而后国定。当是时。国有大丧。祸乱滔天。元何所恃而屹然独立乎。其藉手而见信于人者。不赖宠尔。苏辙谓使元怀禄顾宠。重于出奔。则不能讨。诚哉言乎。
石而后国定。当是时。国有大丧。祸乱滔天。元何所恃而屹然独立乎。其藉手而见信于人者。不赖宠尔。苏辙谓使元怀禄顾宠。重于出奔。则不能讨。诚哉言乎。伊尹放太甲。天下不疑其心。以伊尹不顾千驷之节。孚信于天下也。自百里饭牛以上。出处穷达。祸福利害。世事之千变万化。皆以爵禄不入于心者处之。事事皆肥。
莒人灭鄫。圣人特笔也。或曰。莒女有为鄫夫人。如黄歇,吕不韦事者。或曰。鄫取莒公子为后。或曰。立其甥也。其说不同。而其立异姓为后。神不歆非其类则一也。贾充子黎民蚤死。妻郭槐表充遗意。以外孙韩谧为后。及议充谥。博士秦秀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得春秋之旨也。我国士大夫明于纪度。而或有外孙奉祀。不知其灭亡之祸。憯于兵革。哀哉。
晋,楚为宋之盟。中国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百姓免于兵革之患者。十有馀年。晋赵武,楚屈建之功。不下齐桓。宜圣人善之也。然春秋屡言以著其恶何欤。噫。夷夏之防。万世之义也。兵革之息。一时之利也。天地冠屦之分。内外南北之限。阴阳消长之机。人兽生死之关。皆于宋之会大紊乱。故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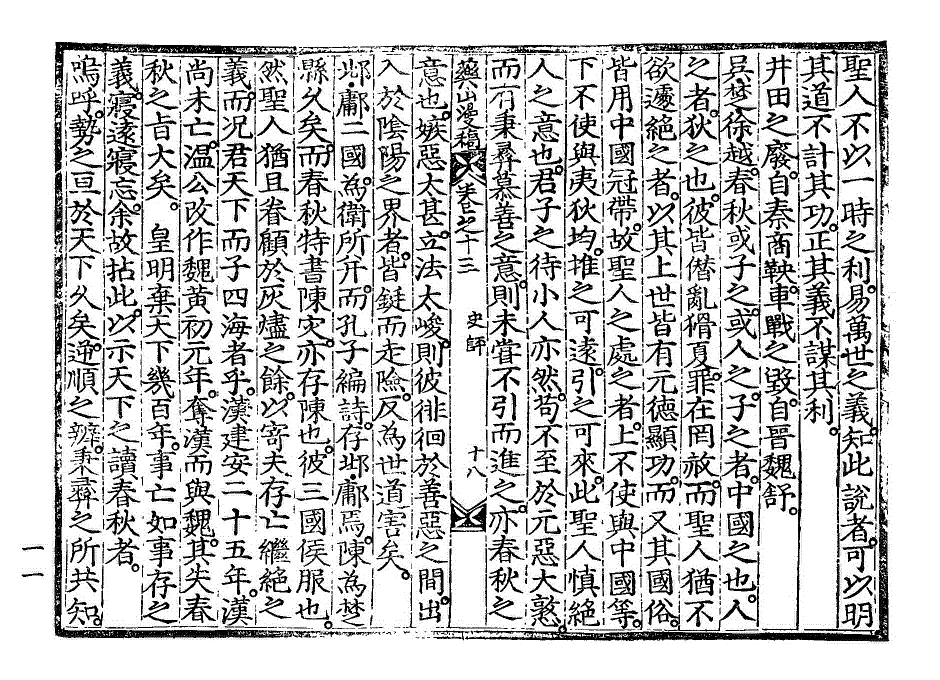 圣人不以一时之利。易万世之义。知此说者。可以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
圣人不以一时之利。易万世之义。知此说者。可以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井田之废。自秦商鞅。车战之毁。自晋魏舒。
吴,楚,徐,越。春秋或子之。或人之。子之者。中国之也。人之者。狄之也。彼皆僭乱猾夏。罪在罔赦。而圣人犹不欲遽绝之者。以其上世皆有元德显功。而又其国俗。皆用中国冠带。故圣人之处之者。上不使与中国等。下不使与夷狄均。推之可远。引之可来。此圣人慎绝人之意也。君子之待小人亦然。苟不至于元恶大憝。而有秉彝慕善之意。则未尝不引而进之。亦春秋之意也。嫉恶太甚。立法太峻。则彼徘徊于善恶之间。出入于阴阳之界者。皆铤而走险。反为世道害矣。
邶,鄘二国。为卫所并。而孔子编诗。存邶,鄘焉。陈为楚县久矣。而春秋特书陈灾。亦存陈也。彼三国侯服也。然圣人犹且眷顾于灰烬之馀。以寄夫存亡继绝之义。而况君天下而子四海者乎。汉建安二十五年。汉尚未亡。温公改作魏黄初元年。夺汉而与魏。其失春秋之旨大矣。 皇明弃天下几百年。事亡如事存之义。寝远寝忘。余故拈此。以示天下之读春秋者。
呜呼。势之亘于天下久矣。逆顺之辨。秉彝之所共知。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2H 页
 而威权所在。从恶如归。则鲁昭公以君伐臣。不克而奔。况以君子之孤根弱植而谋去小人者。不察夫杯水车薪强弱之势。则其能免于陈窦之祸者几希。噫。人君尊如神明。威如雷霆。天下国家之势。伊谁之有。而乃反倒执太阿。颠沛而不自救。哀哉。为人君者。其可假人以利器也哉。
而威权所在。从恶如归。则鲁昭公以君伐臣。不克而奔。况以君子之孤根弱植而谋去小人者。不察夫杯水车薪强弱之势。则其能免于陈窦之祸者几希。噫。人君尊如神明。威如雷霆。天下国家之势。伊谁之有。而乃反倒执太阿。颠沛而不自救。哀哉。为人君者。其可假人以利器也哉。自古阴邪凶孽。亦未尝不假借名义。鲁昭公葬绝兆域。主不祔庙。臣民之至痛也。畏季氏。莫敢言者。及夫阳虎将杀季氏。始以昭公之主从祀太庙。盖欲著季氏之罪。以媚国人。不可以言出阳虎而斥其大义。又不可以假借大义而原恕阳虎。
春秋书齐人归郓,欢,龟阴田。尧舜事业。自尧舜观之。大虚浮云。龟阴尺土。于夫子何有。化工之笔。记实而已。后人以自序其绩。颇费分释。何其眼小。
桓宫,僖宫灾。桓,僖于是亲尽矣。圣人因灾以书。以见不迁之失礼。或曰。祖有功宗有德。僖公有功德可称。夫子非其不迁何欤。曰。太祖创业。于礼不迁。继世之君。虽有功德。非子孙之所可选择。七庙五庙。世尽而迁礼也。孝子慈孙。事其祖考。奚问其功德之有无也。人臣之颂功德上尊号。以媚君上者。固谄谀之臣。而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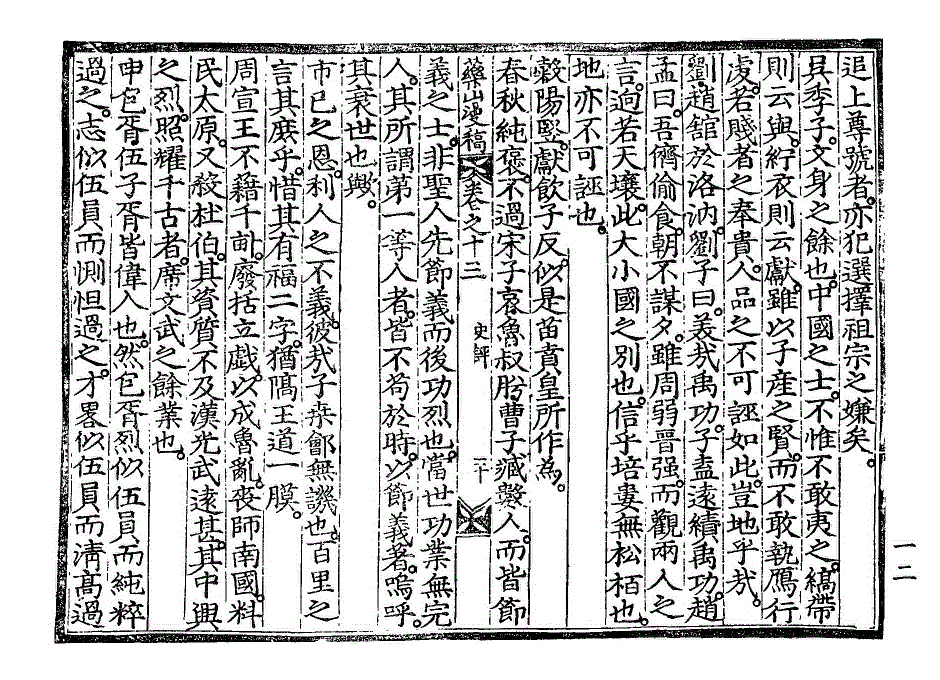 追上尊号者。亦犯选择祖宗之嫌矣。
追上尊号者。亦犯选择祖宗之嫌矣。吴季子。文身之馀也。中国之士。不惟不敢夷之。缟带则云与。纻衣则云献。虽以子产之贤。而不敢执雁行虔。若贱者之奉贵。人品之不可诬如此。岂地乎哉。
刘,赵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子盍远绩禹功。赵孟曰。吾侪偷食。朝不谋夕。虽周弱晋强。而观两人之言。迥若天壤。此大小国之别也。信乎培娄无松柏也。地亦不可诬也。
谷阳竖。献饮子反。似是苗贲皇所作为。
春秋纯褒。不过宋子哀,鲁叔肸,曹子臧数人。而皆节义之士。非圣人先节义而后功烈也。当世功业无完人。其所谓第一等人者。皆不苟于时。以节义著。呜呼。其衰世也欤。
市己之恩。利人之不义。彼哉子桑郐无讥也。百里之言其庶乎。惜其有福二字。犹隔王道一膜。
周宣王不藉千亩。废括立戏。以成鲁乱。丧师南国。料民太原。又杀杜伯。其资质不及汉光武远甚。其中兴之烈。照耀千古者。席文武之馀业也。
申包胥,伍子胥皆伟人也。然包胥烈似伍员而纯粹过之。志似伍员而恻怛过之。才略似伍员而清高过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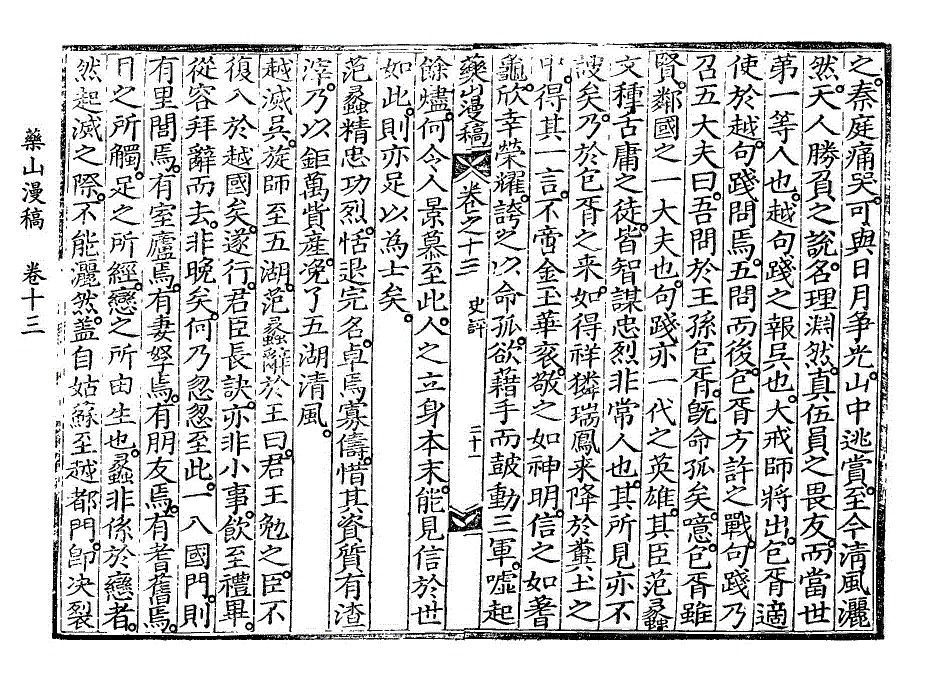 之。秦庭痛哭。可与日月争光。山中逃赏。至今清风洒然。天人胜负之说。名理渊然。真伍员之畏友。而当世第一等人也。越句践之报吴也。大戒师将出。包胥适使于越。句践问焉。五问而后。包胥方许之战。句践乃召五大夫曰。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噫。包胥虽贤。邻国之一大夫也。句践亦一代之英雄。其臣范蠡,文种,舌庸之徒。皆智谋忠烈非常人也。其所见亦不謏矣。乃于包胥之来。如得祥獜瑞凤来降于粪土之中。得其一言。不啻金玉华衮。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欣幸荣耀。誇之以命孤。欲藉手而鼓动三军。嘘起馀烬。何令人景慕至此。人之立身本末。能见信于世如此。则亦足以为士矣。
之。秦庭痛哭。可与日月争光。山中逃赏。至今清风洒然。天人胜负之说。名理渊然。真伍员之畏友。而当世第一等人也。越句践之报吴也。大戒师将出。包胥适使于越。句践问焉。五问而后。包胥方许之战。句践乃召五大夫曰。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噫。包胥虽贤。邻国之一大夫也。句践亦一代之英雄。其臣范蠡,文种,舌庸之徒。皆智谋忠烈非常人也。其所见亦不謏矣。乃于包胥之来。如得祥獜瑞凤来降于粪土之中。得其一言。不啻金玉华衮。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欣幸荣耀。誇之以命孤。欲藉手而鼓动三军。嘘起馀烬。何令人景慕至此。人之立身本末。能见信于世如此。则亦足以为士矣。范蠡精忠功烈。恬退完名。卓焉寡俦。惜其资质有渣滓。乃以钜万赀产。浼了五湖清风。
越灭吴。旋师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于越国矣。遂行。君臣长诀。亦非小事。饮至礼毕。从容拜辞而去。非晚矣。何乃匆匆至此。一入国门。则有里闾焉。有室庐焉。有妻孥焉。有朋友焉。有耆旧焉。目之所触。足之所经。恋之所由生也。蠡非系于恋者。然起灭之际。不能洒然。盖自姑苏至越都门。即决裂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3L 页
 奋迅。慷慨之气之所亘也。自都门至于文台。即徘徊眷顾。依恋之情之所沿也。蠡于此气未熄。此情未生也。一剑快断而行。真万夫不当之勇也。释氏桑下不三宿。亦此意也。蠡尚如此。况下于蠡者。其可牵恋迟回耶。
奋迅。慷慨之气之所亘也。自都门至于文台。即徘徊眷顾。依恋之情之所沿也。蠡于此气未熄。此情未生也。一剑快断而行。真万夫不当之勇也。释氏桑下不三宿。亦此意也。蠡尚如此。况下于蠡者。其可牵恋迟回耶。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魏斯,赵籍,韩虔者。晋之贼臣也。子夏以圣门高弟。亲奉盘于函丈沐浴之时。而索居西河。厌然为魏斯之宾师。田子方又何足诛焉。或曰。孟子何以见齐梁之君也。曰。易世也。君子恶恶。不在后嗣。
田文脱秦。以客之力。楚国万钟。何逊薛笾。君臣恩义。何如宾主。章华庭陛。食君者几人。六千里山河。曾无一个男子脱其君于武关。楚之群臣。皆鸡鸣狗盗之罪人也。
伯夷不食而死。屈原赴水而死。余谓未必然。伯夷无饿死之义。不食者周禄尔。耕而食可也。若绝粒而死。则不合天理。仁者纯然天理之谓也。伯夷求仁得仁。若其死不合天理。则乌得谓之仁。然则孔子谓之伯夷饿于首阳之下者何欤。逃孤竹之封。辞武王之禄。疏食菜羹于荒山穷谷之间者。谓之饿可也。此对齐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4H 页
 景公千驷之富而言也。岂蝉肠雀立而死者乎。饿一转而为饿死。耻食一转而为不食。采薇赋兴。又成绝粒之證。遂使云霞高躅。为原野之僵殍。得仁君子。为索隐行怪之士。以伤清中之太和。甚矣。世人之好怪也。屈原虽不可与伯夷比。而斯亦博学高识。纯忠卓节之士也。匹夫匹妇之自经于沟渎。亦不为也。其所谓葬鱼腹从彭咸。怀沙沉流。似寓言尔。升皇赫戏。岂真登天。揔辔扶桑。岂真拂日。风云雷雨。草木鸟兽。有戎虙妃。高丘二姚。汤谷寒门。四方六漠。至于羽人不死之乡。度世久视之诀。大抵皆寓。何独于鱼腹彭咸而为庄语耶。伯夷之圣。屈原之贤。而史失其传。死生大节。不合正理如此。余甚惜之。此死一洒之也。至于惜往日之阕。辞甚迫隘。余亦疑之。然以正理思之。原必不然。或曰。饿死投渊之失传。既得命矣。叩马事何如。曰。伯夷武王。各遵天理。各行正道。如上山者。各自努力。何与他人事耶。叩马而谏。非伯夷本色。采薇歌。亦后人为之。
景公千驷之富而言也。岂蝉肠雀立而死者乎。饿一转而为饿死。耻食一转而为不食。采薇赋兴。又成绝粒之證。遂使云霞高躅。为原野之僵殍。得仁君子。为索隐行怪之士。以伤清中之太和。甚矣。世人之好怪也。屈原虽不可与伯夷比。而斯亦博学高识。纯忠卓节之士也。匹夫匹妇之自经于沟渎。亦不为也。其所谓葬鱼腹从彭咸。怀沙沉流。似寓言尔。升皇赫戏。岂真登天。揔辔扶桑。岂真拂日。风云雷雨。草木鸟兽。有戎虙妃。高丘二姚。汤谷寒门。四方六漠。至于羽人不死之乡。度世久视之诀。大抵皆寓。何独于鱼腹彭咸而为庄语耶。伯夷之圣。屈原之贤。而史失其传。死生大节。不合正理如此。余甚惜之。此死一洒之也。至于惜往日之阕。辞甚迫隘。余亦疑之。然以正理思之。原必不然。或曰。饿死投渊之失传。既得命矣。叩马事何如。曰。伯夷武王。各遵天理。各行正道。如上山者。各自努力。何与他人事耶。叩马而谏。非伯夷本色。采薇歌。亦后人为之。荀卿论兵要曰。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带剑。赢三日粮。日中而趍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气力数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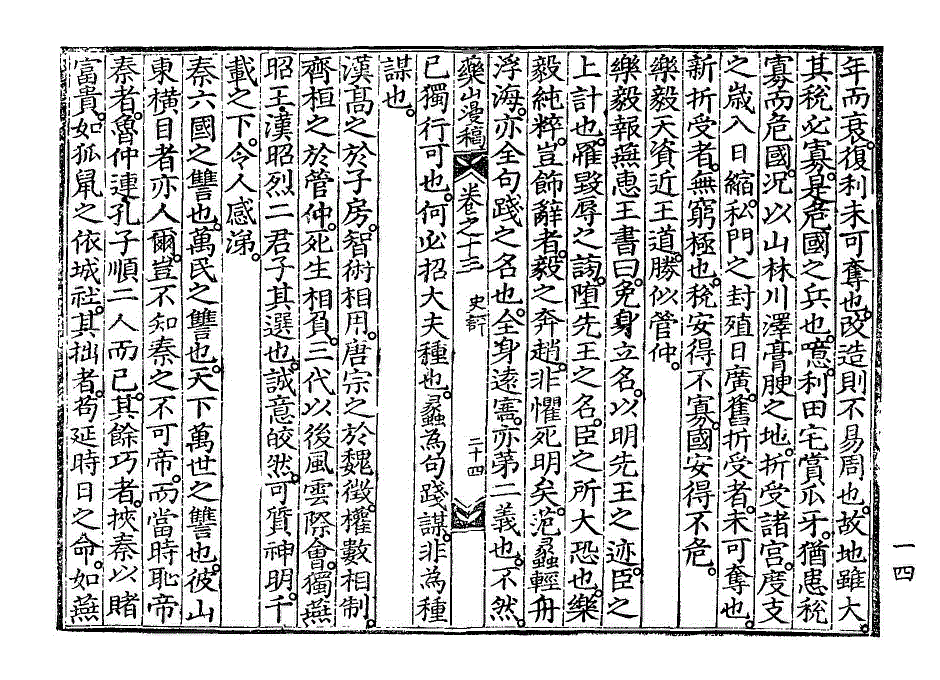 年而衰。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噫。利田宅赏爪牙。犹患税寡而危国。况以山林川泽膏腴之地。折受诸宫。度支之岁入日缩。私门之封殖日广。旧折受者。未可夺也。新折受者。无穷极也。税安得不寡。国安得不危。
年而衰。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噫。利田宅赏爪牙。犹患税寡而危国。况以山林川泽膏腴之地。折受诸宫。度支之岁入日缩。私门之封殖日广。旧折受者。未可夺也。新折受者。无穷极也。税安得不寡。国安得不危。乐毅天资近王道。胜似管仲。
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免身立名。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罹毁辱之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乐毅纯粹。岂饰辞者。毅之奔赵。非惧死明矣。范蠡轻舟浮海。亦全句践之名也。全身远害。亦第二义也。不然。已独行可也。何必招大夫种也。蠡为句践谋。非为种谋也。
汉高之于子房。智术相用。唐宗之于魏徵。权数相制。齐桓之于管仲。死生相负。三代以后风云际会。独燕昭王,汉昭烈二君子其选也。诚意皎然。可质神明。千载之下。令人感涕。
秦六国之雠也。万民之雠也。天下万世之雠也。彼山东横目者亦人尔。岂不知秦之不可帝。而当时耻帝秦者。鲁仲连,孔子顺二人而已。其馀巧者。挟秦以赌富贵。如狐鼠之依城社。其拙者。苟延时日之命。如燕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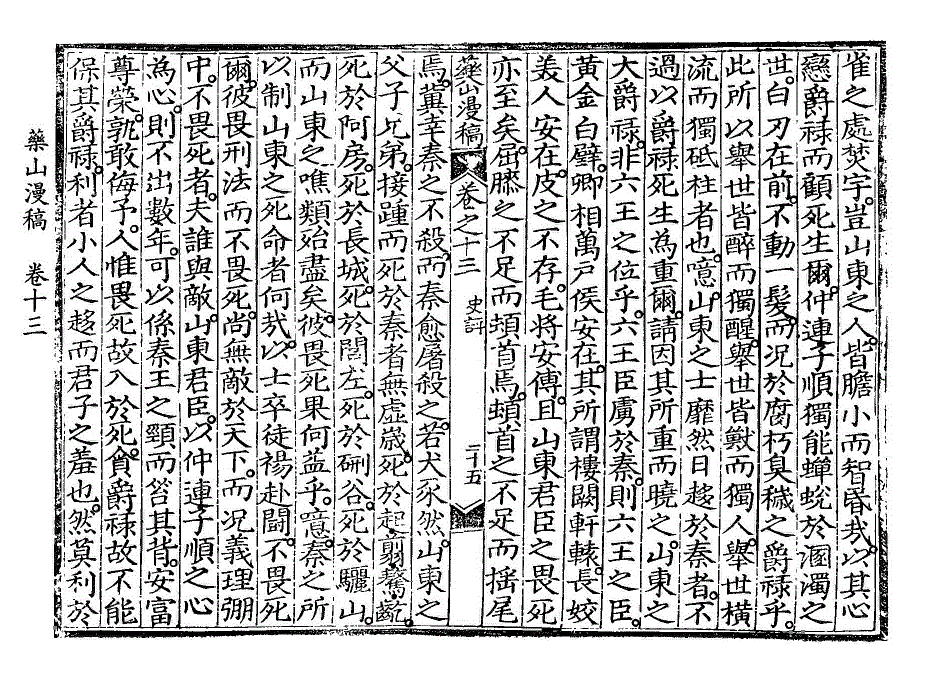 雀之处焚宇。岂山东之人。皆胆小而智昏哉。以其心恋爵禄而顾死生尔。仲连,子顺独能蝉蜕于溷浊之世。白刃在前。不动一发。而况于腐朽臭秽之爵禄乎。此所以举世皆醉而独醒。举世皆兽而独人。举世横流而独砥柱者也。噫。山东之士靡然日趍于秦者。不过以爵禄死生为重尔。请因其所重而晓之。山东之大爵禄。非六王之位乎。六王臣虏于秦。则六王之臣。黄金白璧。卿相万户侯安在。其所谓楼阙轩辕。长姣美人安在。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且山东君臣之畏死亦至矣。屈膝之不足而顿首焉。顿首之不足而摇尾焉。冀幸秦之不杀。而秦愈屠杀之。若犬豕然。山东之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无虚岁。死于起,剪,骜,龁。死于阿房。死于长城。死于闾左。死于硎谷。死于骊山。而山东之噍类殆尽矣。彼畏死果何益乎。噫。秦之所以制山东之死命者何哉。以士卒徒裼赴斗。不畏死尔。彼畏刑法而不畏死。尚无敌于天下。而况义理弸中。不畏死者。夫谁与敌。山东君臣。以仲连,子顺之心为心。则不出数年。可以系秦王之颈而笞其背。安富尊荣。孰敢侮予。人惟畏死故入于死。贪爵禄故不能保其爵禄。利者小人之趍而君子之羞也。然莫利于
雀之处焚宇。岂山东之人。皆胆小而智昏哉。以其心恋爵禄而顾死生尔。仲连,子顺独能蝉蜕于溷浊之世。白刃在前。不动一发。而况于腐朽臭秽之爵禄乎。此所以举世皆醉而独醒。举世皆兽而独人。举世横流而独砥柱者也。噫。山东之士靡然日趍于秦者。不过以爵禄死生为重尔。请因其所重而晓之。山东之大爵禄。非六王之位乎。六王臣虏于秦。则六王之臣。黄金白璧。卿相万户侯安在。其所谓楼阙轩辕。长姣美人安在。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且山东君臣之畏死亦至矣。屈膝之不足而顿首焉。顿首之不足而摇尾焉。冀幸秦之不杀。而秦愈屠杀之。若犬豕然。山东之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无虚岁。死于起,剪,骜,龁。死于阿房。死于长城。死于闾左。死于硎谷。死于骊山。而山东之噍类殆尽矣。彼畏死果何益乎。噫。秦之所以制山东之死命者何哉。以士卒徒裼赴斗。不畏死尔。彼畏刑法而不畏死。尚无敌于天下。而况义理弸中。不畏死者。夫谁与敌。山东君臣。以仲连,子顺之心为心。则不出数年。可以系秦王之颈而笞其背。安富尊荣。孰敢侮予。人惟畏死故入于死。贪爵禄故不能保其爵禄。利者小人之趍而君子之羞也。然莫利于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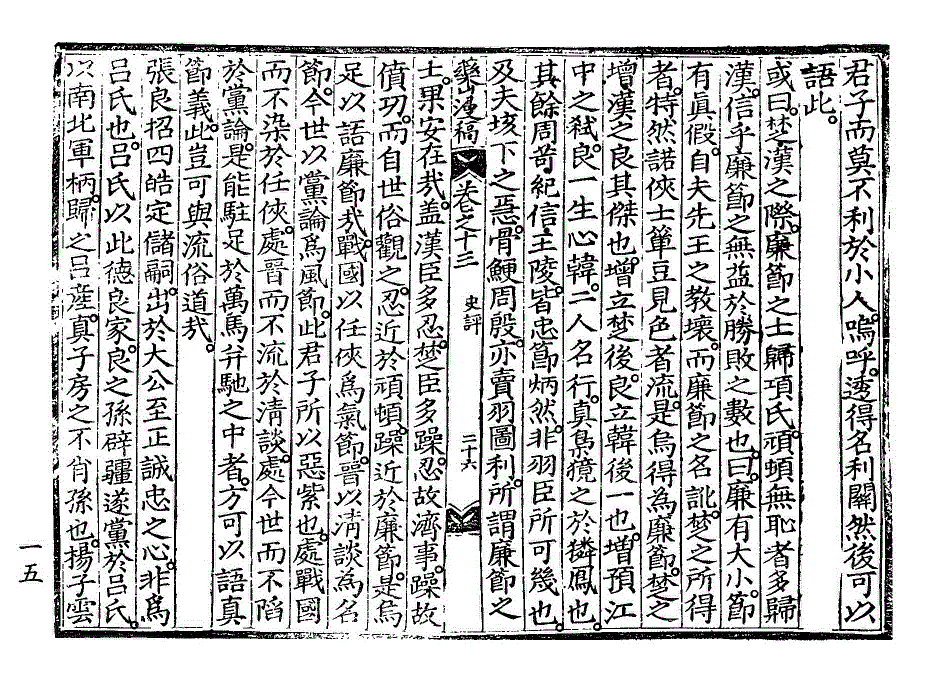 君子而莫不利于小人。呜呼。透得名利关然后可以语此。
君子而莫不利于小人。呜呼。透得名利关然后可以语此。或曰。楚,汉之际。廉节之士归项氏。顽顿无耻者多归汉。信乎廉节之无益于胜败之数也。曰。廉有大小。节有真假。自夫先王之教坏。而廉节之名讹。楚之所得者。特然诺侠士箪豆见色者流。是乌得为廉节。楚之增,汉之良其杰也。增立楚后。良立韩后一也。增预江中之弑。良一生心韩。二人名行。真枭獍之于麟凤也。其馀周苛,纪信,王陵。皆忠节炳然。非羽臣所可几也。及夫垓下之急。骨鲠周殷。亦卖羽图利。所谓廉节之士。果安在哉。盖汉臣多忍。楚臣多躁。忍故济事。躁故偾功。而自世俗观之。忍近于顽顿。躁近于廉节。是乌足以语廉节哉。战国以任侠为气节。晋以清谈为名节。今世以党论为风节。此君子所以恶紫也。处战国而不染于任侠。处晋而不流于清谈。处今世而不陷于党论。是能驻足于万马并驰之中者。方可以语真节义。此岂可与流俗道哉。
张良招四皓定储嗣。出于大公至正诚忠之心。非为吕氏也。吕氏以此德良家。良之孙辟疆遂党于吕氏。以南北军柄。归之吕产。真子房之不肖孙也。杨子云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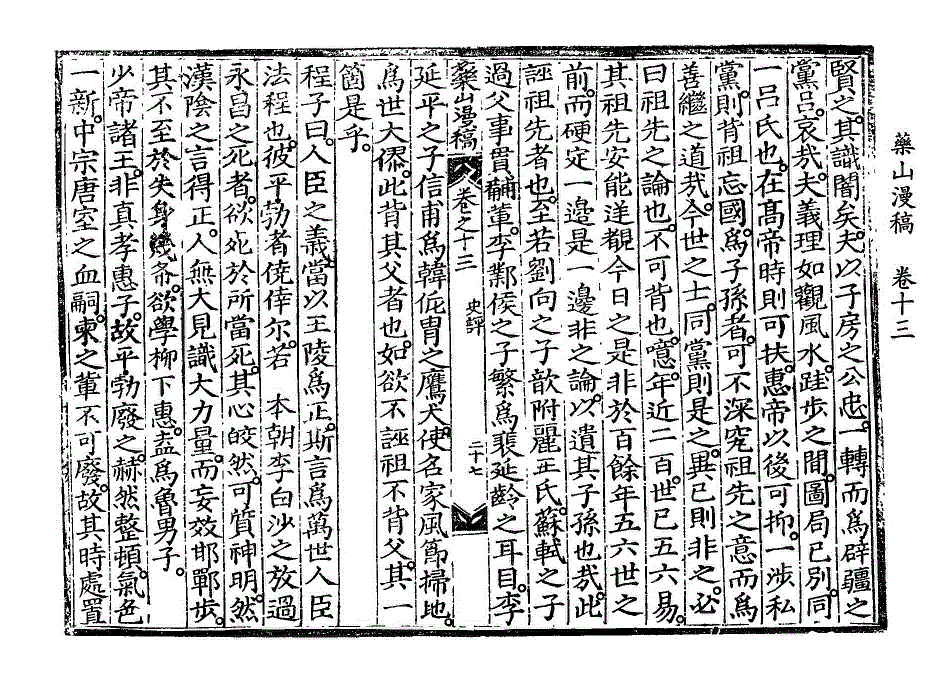 贤之。其识闇矣。夫以子房之公忠。一转而为辟疆之党吕。哀哉。夫义理如观风水。跬步之间。图局已别。同一吕氏也。在高帝时则可扶。惠帝以后可抑。一涉私党。则背祖忘国。为子孙者。可不深究祖先之意而为善继之道哉。今世之士。同党则是之。异己则非之。必曰祖先之论也。不可背也。噫。年近二百。世已五六易。其祖先安能逆睹今日之是非于百馀年五六世之前。而硬定一边是一边非之论。以遗其子孙也哉。此诬祖先者也。至若刘向之子歆附丽王氏。苏轼之子过父事贯黼辈。李邺侯之子繁为裴延龄之耳目。李延平之子信甫为韩侂胄之鹰犬。使名家风节扫地。为世大僇。此背其父者也。如欲不诬祖不背父。其一个是乎。
贤之。其识闇矣。夫以子房之公忠。一转而为辟疆之党吕。哀哉。夫义理如观风水。跬步之间。图局已别。同一吕氏也。在高帝时则可扶。惠帝以后可抑。一涉私党。则背祖忘国。为子孙者。可不深究祖先之意而为善继之道哉。今世之士。同党则是之。异己则非之。必曰祖先之论也。不可背也。噫。年近二百。世已五六易。其祖先安能逆睹今日之是非于百馀年五六世之前。而硬定一边是一边非之论。以遗其子孙也哉。此诬祖先者也。至若刘向之子歆附丽王氏。苏轼之子过父事贯黼辈。李邺侯之子繁为裴延龄之耳目。李延平之子信甫为韩侂胄之鹰犬。使名家风节扫地。为世大僇。此背其父者也。如欲不诬祖不背父。其一个是乎。程子曰。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斯言为万世人臣法程也。彼平,勃者侥倖尔。若 本朝李白沙之放过永昌之死者。欲死于所当死。其心皎然。可质神明。然汉阴之言得正。人无大见识大力量。而妄效邯郸步。其不至于失身几希。欲学柳下惠。盍为鲁男子。
少帝诸王。非真孝惠子。故平,勃废之。赫然整顿。气色一新。中宗唐室之血嗣。柬之辈不可废。故其时处置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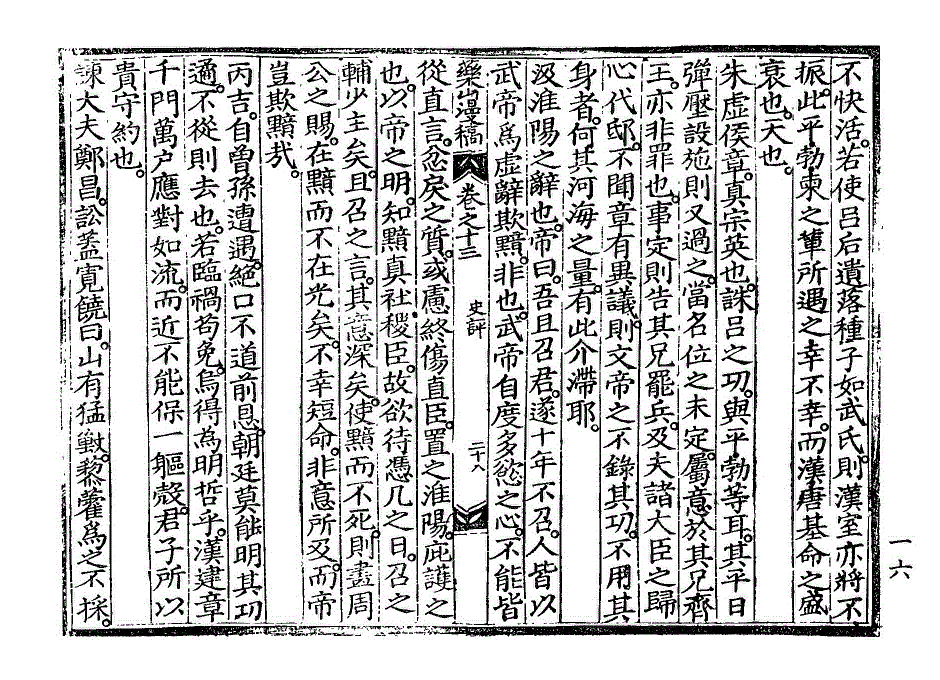 不快活。若使吕后遗落种子如武氏。则汉室亦将不振。此平,勃,柬之辈所遇之幸不幸。而汉,唐基命之盛衰也。天也。
不快活。若使吕后遗落种子如武氏。则汉室亦将不振。此平,勃,柬之辈所遇之幸不幸。而汉,唐基命之盛衰也。天也。朱虚侯章。真宗英也。诛吕之功。与平,勃等耳。其平日弹压设施则又过之。当名位之未定。属意于其兄齐王。亦非罪也。事定则告其兄罢兵。及夫诸大臣之归心代邸。不闻章有异议。则文帝之不录其功。不用其身者。何其河海之量。有此介滞耶。
汲淮阳之辞也。帝曰。吾且召君。遂十年不召。人皆以武帝为虚辞欺黯。非也。武帝自度多欲之心。不能皆从直言。忿戾之质。或虑终伤直臣。置之淮阳。庇护之也。以帝之明。知黯真社稷臣。故欲待凭几之日。召之辅少主矣。且召之言。其意深矣。使黯而不死。则画周公之赐。在黯而不在光矣。不幸短命。非意所及。而帝岂欺黯哉。
丙吉。自曾孙遭遇。绝口不道前恩。朝廷莫能明其功遹。不从则去也。若临祸苟免。乌得为明哲乎。汉建章千门万户应对如流。而近不能保一躯壳。君子所以贵守约也。
谏大夫郑昌。讼盖宽饶曰。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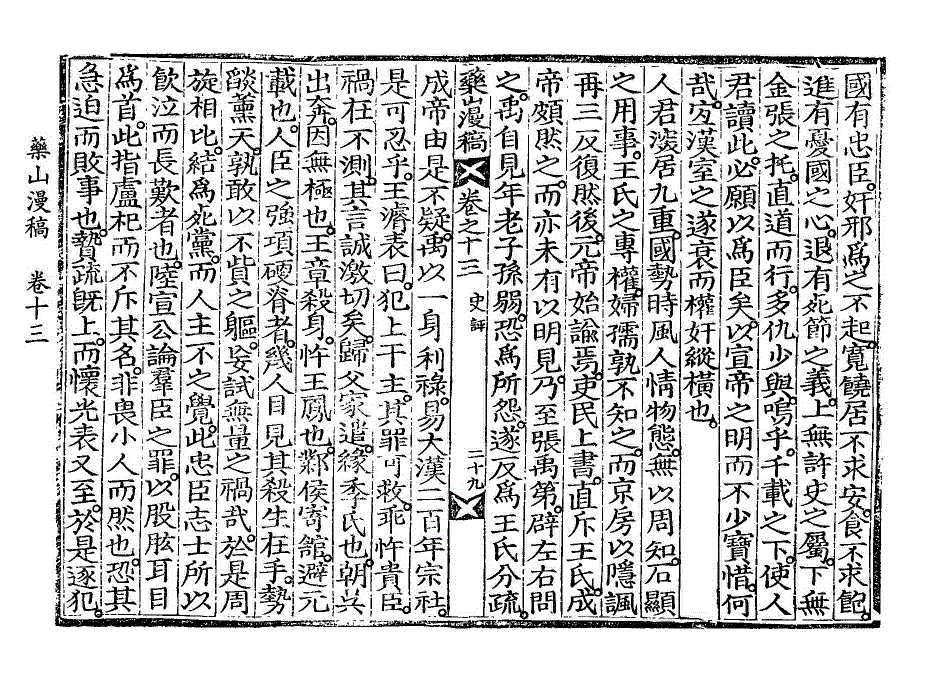 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呜乎。千载之下。使人君读此。必愿以为臣矣。以宣帝之明而不少宝惜。何哉。宜汉室之遂衰而权奸纵横也。
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呜乎。千载之下。使人君读此。必愿以为臣矣。以宣帝之明而不少宝惜。何哉。宜汉室之遂衰而权奸纵横也。人君深居九重。国势时风人情物态。无以周知。石显之用事。王氏之专权。妇孺孰不知之。而京房以隐讽再三反复然后。元帝始谕焉。吏民上书。直斥王氏。成帝颇然之。而亦未有以明见。乃至张禹第。辟左右问之。禹自见年老子孙弱。恐为所怨。遂反为王氏分疏。成帝由是不疑。禹以一身利禄。易大汉二百年宗社。是可忍乎。王浚表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其言诚激切矣。归父家遣。缘季氏也。朝吴出奔。因无极也。王章杀身。忤王凤也。邺侯寄馆。避元载也。人臣之强项硬脊者。几人目见其杀生在手。势燄薰天。孰敢以不赀之躯。妄试无量之祸哉。于是周旋相比。结为死党。而人主不之觉。此忠臣志士所以饮泣而长叹者也。陆宣公论群臣之罪。以股肱耳目为首。此指卢杞而不斥其名。非畏小人而然也。恐其急迫而败事也。贽疏既上。而怀光表又至。于是逐犯。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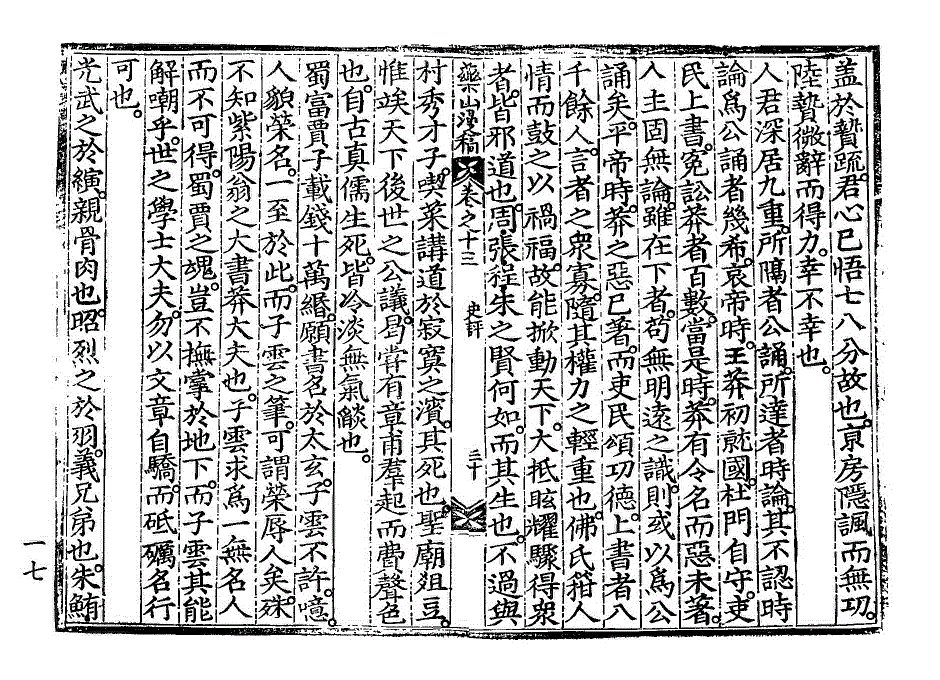 盖于贽疏。君心已悟七八分故也。京房隐讽而无功。陆贽微辞而得力。幸不幸也。
盖于贽疏。君心已悟七八分故也。京房隐讽而无功。陆贽微辞而得力。幸不幸也。人君深居九重。所隔者公诵。所达者时论。其不认时论为公诵者几希。哀帝时。王莽初就国。杜门自守。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当是时。莽有令名而恶未著。人主固无论。虽在下者。苟无明远之识。则或以为公诵矣。平帝时。莽之恶已著。而吏民颂功德。上书者八千馀人。言者之众寡。随其权力之轻重也。佛氏钳人情而鼓之以祸福。故能掀动天下。大抵眩耀骤得众者。皆邪道也。周,张,程,朱之贤何如。而其生也。不过与村秀才子。吃菜讲道于寂寞之滨。其死也。圣庙俎豆。惟俟天下后世之公议。曷尝有章甫群起而费声色也。自古真儒生死。皆冷淡无气燄也。
蜀富贾子载钱十万缗。愿书名于太玄。子云不许。噫。人貌荣名。一至于此。而子云之笔。可谓荣辱人矣。殊不知紫阳翁之大书莽大夫也。子云求为一无名人而不可得。蜀贾之魂。岂不抚掌于地下。而子云其能解嘲乎。世之学士大夫。勿以文章自骄。而砥砺名行可也。
光武之于演。亲骨肉也。昭烈之于羽。义兄弟也。朱鲔,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8H 页
 孙权。其雠也。光武赦鲔而速洛阳之降。昭烈征权而误天下之势。其果孰得孰失。曰皆失之矣。鲔之杀演。同室之推刃也。权之杀羽。越人之弯弓也。权可姑释。而鲔不可赦也。鲔虽不赦。而洛阳终可下也。权若不释。则天下不可定也。光武自得于天下之归而忘其兄之至冤。昭烈不忍于气义之激而忽讨复之大计。光武天资不及昭烈。昭烈才略不及光武。论其失则昭烈大矣。
孙权。其雠也。光武赦鲔而速洛阳之降。昭烈征权而误天下之势。其果孰得孰失。曰皆失之矣。鲔之杀演。同室之推刃也。权之杀羽。越人之弯弓也。权可姑释。而鲔不可赦也。鲔虽不赦。而洛阳终可下也。权若不释。则天下不可定也。光武自得于天下之归而忘其兄之至冤。昭烈不忍于气义之激而忽讨复之大计。光武天资不及昭烈。昭烈才略不及光武。论其失则昭烈大矣。善哉言乎。福兮𥚁所倚。𥚁兮福所倚。又曰。其毁也成。其成也毁。又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又曰。惟圣罔念作狂。邓禹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曰。后世必有兴者。其后邓后登壸位有令德。子孙崇极富贵。此世称福者。其后邓后兄弟骘,悝,弘,阊。皆不免诛戮。𥚁及宗族。没入赀产。吾见其祸而不见其福也。吾见其毁而不见其成也。后称戚畹之贤。必曰马邓。称后妃之德。必曰马邓。而弘,骘,恭俭。暮年寝衰。袁敞以不阿邓氏死。岂非作法于凉。其弊犹贪者耶。和熹淑德。晚节或疵。杜根以请释权柄几死。岂非惟圣罔念作狂者耶。瓜葛皇家者。云胡不戒。
黄宪是东汉人物之首。然无著述传后。故范晔曰。黄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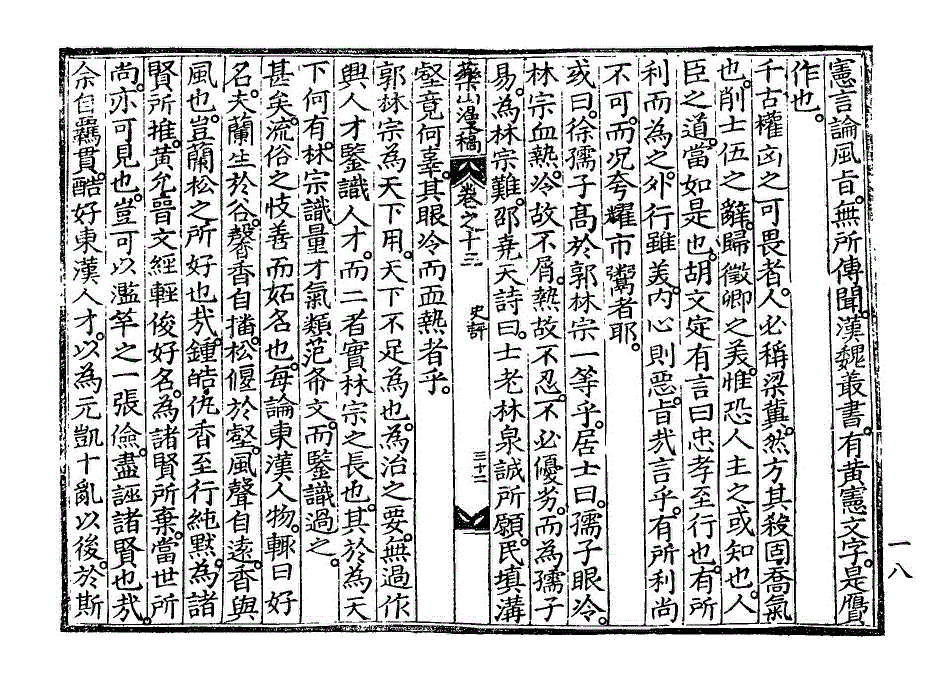 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汉魏丛书。有黄宪文字。是赝作也。
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汉魏丛书。有黄宪文字。是赝作也。千古权凶之可畏者。人必称梁冀。然方其杀固,乔气也。削士伍之辞。归徵卿之美。惟恐人主之或知也。人臣之道。当如是也。胡文定有言曰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为之。外行虽美。内心则恶。旨哉言乎。有所利尚不可。而况夸耀市鬻者耶。
或曰。徐孺子高于郭林宗一等乎。居士曰。孺子眼冷。林宗血热。冷故不屑。热故不忍。不必优劣。而为孺子易。为林宗难。邵尧天诗曰。士老林泉诚所愿。民填沟壑竟何辜。其眼冷而血热者乎。
郭林宗为天下用。天下不足为也。为治之要。无过作兴人才鉴识人才。而二者实林宗之长也。其于为天下何有。林宗识量才气类范希文。而鉴识过之。
甚矣。流俗之忮善而妒名也。每论东汉人物。辄曰好名。夫兰生于谷。馨香自播。松偃于壑。风声自远。香与风也。岂兰松之所好也哉。钟皓,仇香至行纯默。为诸贤所推。黄允,晋文经轻俊好名。为诸贤所弃。当世所尚。亦可见也。岂可以滥竽之一张俭。尽诬诸贤也哉。余自羁贯。酷好东汉人才。以为元凯十乱以后。于斯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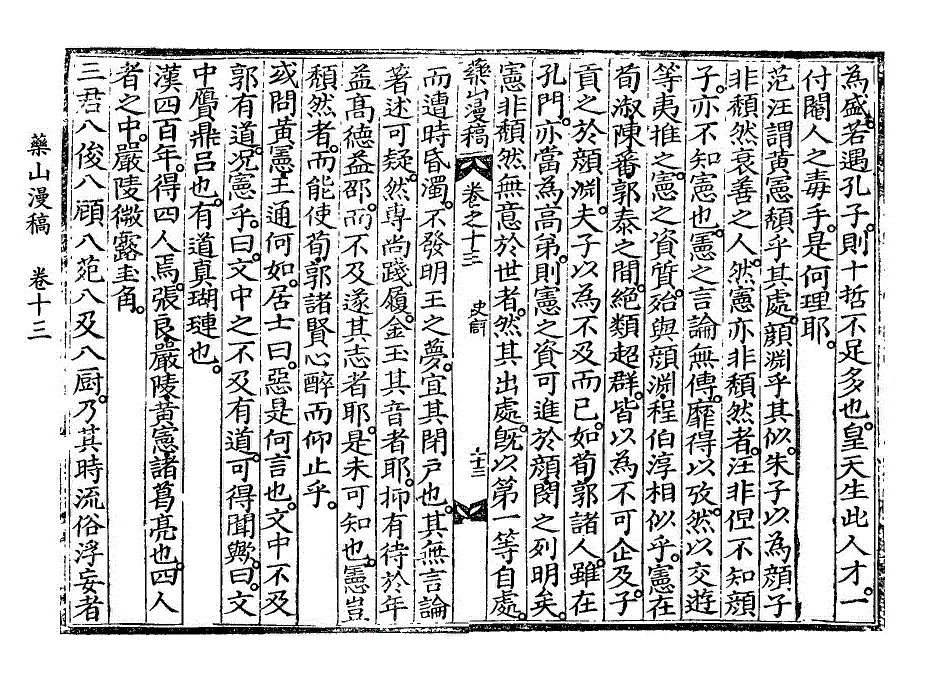 为盛。若遇孔子。则十哲不足多也。皇天生此人才。一付阉人之毒手。是何理耶。
为盛。若遇孔子。则十哲不足多也。皇天生此人才。一付阉人之毒手。是何理耶。范汪谓黄宪颓乎其处。颜渊乎其似。朱子以为颜子非颓然衰善之人。然宪亦非颓然者。汪非但不知颜子。亦不知宪也。宪之言论无传。靡得以考。然以交游等夷推之。宪之资质。殆与颜渊,程伯淳相似乎。宪在荀淑,陈蕃,郭泰之间。绝类超群。皆以为不可企及。子贡之于颜渊。夫子以为不及而已。如荀,郭诸人。虽在孔门。亦当为高弟。则宪之资可进于颜,闵之列明矣。宪非颓然无意于世者。然其出处。既以第一等自处。而遭时昏浊。不发明王之梦。宜其闭户也。其无言论著述可疑。然专尚践履。金玉其音者耶。抑有待于年益高德益卲。而不及遂其志者耶。是未可知也。宪岂颓然者。而能使荀,郭诸贤心醉而仰止乎。
或问黄宪,王通何如。居士曰。恶是何言也。文中不及郭有道。况宪乎。曰。文中之不及有道。可得闻欤。曰。文中赝鼎吕也。有道真瑚琏也。
汉四百年。得四人焉。张良,严陵,黄宪,诸葛亮也。四人者之中。严陵微露圭角。
三君八俊八顾八苑八及八厨。乃其时流俗浮妄者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19L 页
 为之目也。非诸君子意也。度尚卖张磐欺君上。士类所不齿。岂可为八厨之首。其馀猥杂甚多。且如徐稚,仇香,符融,申屠磻之徒。皆士类高品而不与焉。皇甫规,张奂。虽不敢与徐,仇比。若视诸度尚。不亦天壤。而舍此取彼妄矣。张俭亦自攘臂自呈于士类间者。非郭有道诸人所奖许也。
为之目也。非诸君子意也。度尚卖张磐欺君上。士类所不齿。岂可为八厨之首。其馀猥杂甚多。且如徐稚,仇香,符融,申屠磻之徒。皆士类高品而不与焉。皇甫规,张奂。虽不敢与徐,仇比。若视诸度尚。不亦天壤。而舍此取彼妄矣。张俭亦自攘臂自呈于士类间者。非郭有道诸人所奖许也。好名之目。不惟流俗人不喜。为君子者亦病之。然名之好不好。实为善恶生死路头。予观东汉马融初年。清脩溪刻。砥砺名节。及饥困甚。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咫尺之守。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于是出应梁氏之辟。戕杀忠贤。贪污狼藉。其初年砥砺。非真乐善。乃好名也。晚节贪污。非欲为恶。不好名也。善哉倪元璐之言曰。天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行己。宁在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背叛名义。毁裂廉隅者多矣。
西汉之末。人心失去就。或袁或曹。卓然先知汉贼之分者。臧弘是已。
君子归于名义。小人趍于利势。君子寡小人众。宜利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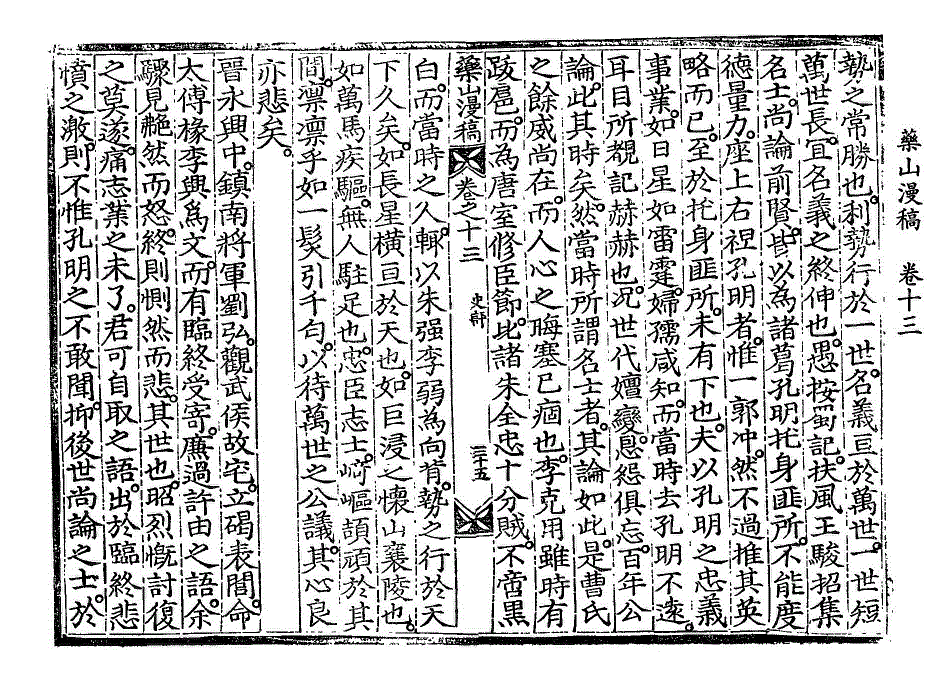 势之常胜也。利势行于一世。名义亘于万世。一世短万世长。宜名义之终伸也。愚按蜀记。扶风王骏招集名士。尚论前贤。皆以为诸葛孔明托身匪所。不能度德量力。座上右袒孔明者。惟一郭冲。然不过推其英略而已。至于托身匪所。未有下也。夫以孔明之忠义事业。如日星如雷霆。妇孺咸知。而当时去孔明不远。耳目所睹记赫赫也。况世代嬗变。恩怨俱忘。百年公论。此其时矣。然当时所谓名士者。其论如此。是曹氏之馀威尚在。而人心之晦塞已痼也。李克用虽时有跋扈。而为唐室修臣节。比诸朱全忠十分贼。不啻黑白。而当时之人。辄以朱强李弱为向背。势之行于天下久矣。如长星横亘于天也。如巨浸之怀山襄陵也。如万马疾驱。无人驻足也。忠臣志士。崎岖颉颃于其间。凛凛乎如一发引千匀。以待万世之公议。其心良亦悲矣。
势之常胜也。利势行于一世。名义亘于万世。一世短万世长。宜名义之终伸也。愚按蜀记。扶风王骏招集名士。尚论前贤。皆以为诸葛孔明托身匪所。不能度德量力。座上右袒孔明者。惟一郭冲。然不过推其英略而已。至于托身匪所。未有下也。夫以孔明之忠义事业。如日星如雷霆。妇孺咸知。而当时去孔明不远。耳目所睹记赫赫也。况世代嬗变。恩怨俱忘。百年公论。此其时矣。然当时所谓名士者。其论如此。是曹氏之馀威尚在。而人心之晦塞已痼也。李克用虽时有跋扈。而为唐室修臣节。比诸朱全忠十分贼。不啻黑白。而当时之人。辄以朱强李弱为向背。势之行于天下久矣。如长星横亘于天也。如巨浸之怀山襄陵也。如万马疾驱。无人驻足也。忠臣志士。崎岖颉颃于其间。凛凛乎如一发引千匀。以待万世之公议。其心良亦悲矣。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观武侯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为文。而有临终受寄。廉过许由之语。余骤见艴然而怒。终则恻然而悲。其世也。昭烈慨讨复之莫遂。痛志业之未了。君可自取之语。出于临终悲愤之激。则不惟孔明之不敢闻。抑后世尚论之士。于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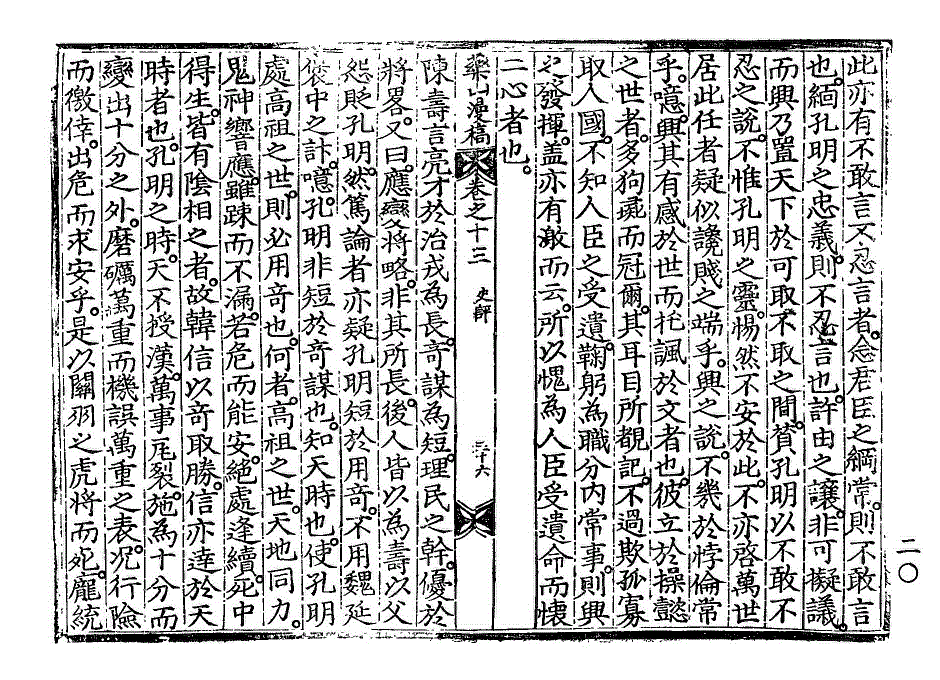 此亦有不敢言不忍言者。念君臣之纲常。则不敢言也。缅孔明之忠义。则不忍言也。许由之让。非可拟议。而兴乃置天下于可取不取之间。赞孔明以不敢不忍之说。不惟孔明之灵。惕然不安于此。不亦启万世居此任者疑似谗贱之端乎。兴之说。不几于悖伦常乎。噫。兴其有感于世而托讽于文者也。彼立于操懿之世者。多狗彘而冠尔。其耳目所睹记。不过欺孤寡取人国。不知人臣之受遗。鞠躬为职分内常事。则兴之发挥。盖亦有激而云。所以愧为人臣受遗命而怀二心者也。
此亦有不敢言不忍言者。念君臣之纲常。则不敢言也。缅孔明之忠义。则不忍言也。许由之让。非可拟议。而兴乃置天下于可取不取之间。赞孔明以不敢不忍之说。不惟孔明之灵。惕然不安于此。不亦启万世居此任者疑似谗贱之端乎。兴之说。不几于悖伦常乎。噫。兴其有感于世而托讽于文者也。彼立于操懿之世者。多狗彘而冠尔。其耳目所睹记。不过欺孤寡取人国。不知人臣之受遗。鞠躬为职分内常事。则兴之发挥。盖亦有激而云。所以愧为人臣受遗命而怀二心者也。陈寿言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后人皆以为寿以父怨贬孔明。然笃论者亦疑孔明短于用奇。不用魏延褒中之计。噫。孔明非短于奇谋也。知天时也。使孔明处高祖之世。则必用奇也。何者。高祖之世。天地同力。鬼神响应。虽疏而不漏。若危而能安。绝处逢续。死中得生。皆有阴相之者。故韩信以奇取胜。信亦达于天时者也。孔明之时。天不授汉。万事瓦裂。施为十分而变出十分之外。磨砺万重而机误万重之表。况行险而徼倖。出危而求安乎。是以关羽之虎将而死。庞统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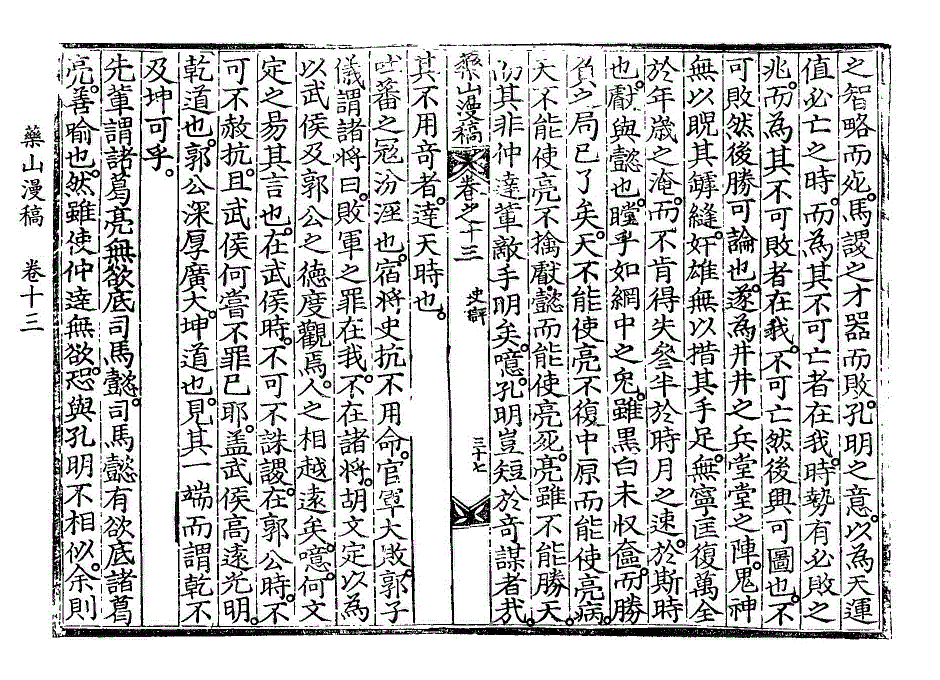 之智略而死。马谡之才器而败。孔明之意。以为天运值必亡之时。而为其不可亡者在我。时势有必败之兆。而为其不可败者在我。不可亡然后兴可图也。不可败然后胜可论也。遂为井井之兵堂堂之阵。鬼神无以睨其罅缝。奸雄无以措其手足。无宁匡复万全于年岁之淹。而不肯得失参半于时月之速。于斯时也。睿与懿也。瞠乎如网中之兔。虽黑白未收奁。而胜负之局已了矣。天不能使亮不复中原而能使亮病。天不能使亮不擒睿,懿而能使亮死。亮虽不能胜天。而其非仲达辈敌手明矣。噫。孔明岂短于奇谋者哉。其不用奇者。达天时也。
之智略而死。马谡之才器而败。孔明之意。以为天运值必亡之时。而为其不可亡者在我。时势有必败之兆。而为其不可败者在我。不可亡然后兴可图也。不可败然后胜可论也。遂为井井之兵堂堂之阵。鬼神无以睨其罅缝。奸雄无以措其手足。无宁匡复万全于年岁之淹。而不肯得失参半于时月之速。于斯时也。睿与懿也。瞠乎如网中之兔。虽黑白未收奁。而胜负之局已了矣。天不能使亮不复中原而能使亮病。天不能使亮不擒睿,懿而能使亮死。亮虽不能胜天。而其非仲达辈敌手明矣。噫。孔明岂短于奇谋者哉。其不用奇者。达天时也。吐蕃之寇汾泾也。宿将史抗不用命。官军大败。郭子仪谓诸将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胡文定以为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观焉。人之相越远矣。噫。何文定之易其言也。在武侯时。不可不诛谡。在郭公时。不可不赦抗。且武侯何尝不罪己耶。盖武侯高远光明。乾道也。郭公深厚广大。坤道也。见其一端而谓乾不及坤可乎。
先辈谓诸葛亮无欲底司马懿。司马懿有欲底诸葛亮。善喻也。然虽使仲达无欲。恐与孔明不相似。余则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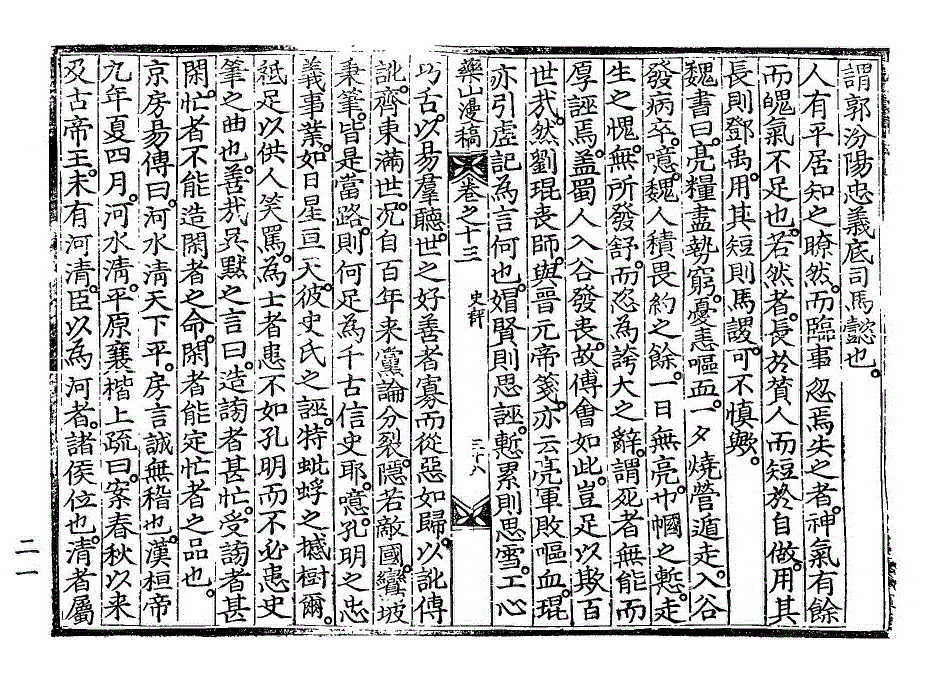 谓郭汾阳忠义底司马懿也。
谓郭汾阳忠义底司马懿也。人有平居知之瞭然。而临事忽焉失之者。神气有馀而魄气不足也。若然者。长于赞人而短于自做。用其长则邓禹。用其短则马谡。可不慎欤。
魏书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发病卒。噫。魏人积畏约之馀。一日无亮。巾帼之惭。走生之愧。无所发舒。而恣为誇大之辞。谓死者无能而厚诬焉。盖蜀人入谷发丧。故傅会如此。岂足以欺百世哉。然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云亮军败呕血。琨亦引虚记为言何也。媢贤则思诬。惭累则思雪。工心巧舌。以易群听。世之好善者寡而从恶如归。以讹传讹。齐东满世。况自百年来党论分裂。隐若敌国。鸾坡秉笔。皆是当路。则何足为千古信史耶。噫。孔明之忠义事业。如日星亘天。彼史氏之诬。特蚍蜉之撼树尔。祗足以供人笑骂。为士者患不如孔明而不必患史笔之曲也。善哉吴默之言曰。造谤者甚忙。受谤者甚闲。忙者不能造闲者之命。闲者能定忙者之品也。
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房言诚无稽也。汉桓帝九年夏四月。河水清。平原襄楷上疏曰。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
药山漫稿卷之十三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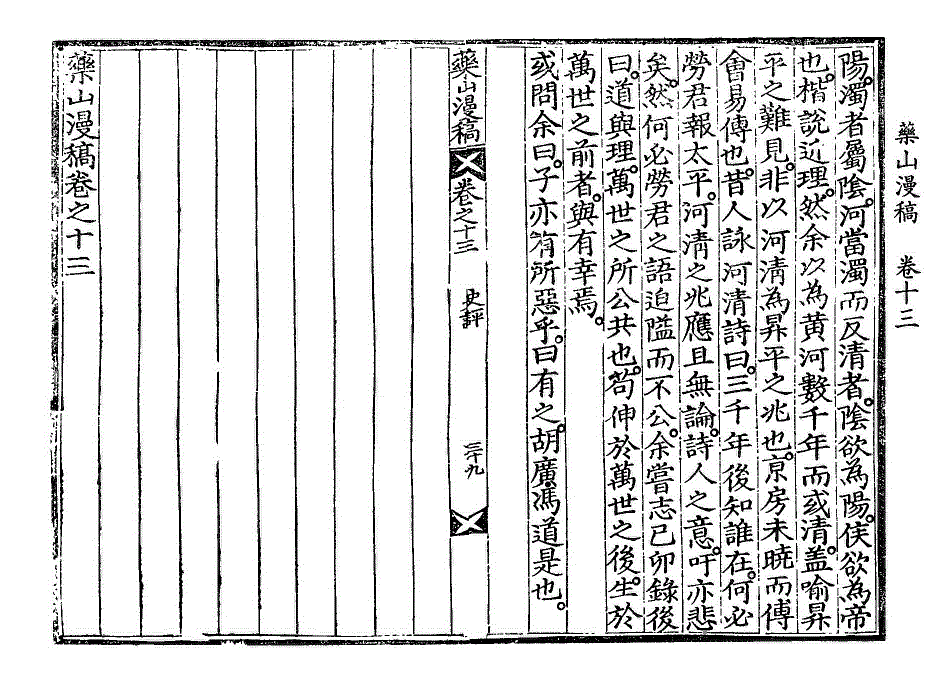 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侯欲为帝也。楷说近理。然余以为黄河数千年而或清。盖喻升平之难见。非以河清为升平之兆也。京房未晓而傅会易传也。昔人咏河清诗曰。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河清之兆应且无论。诗人之意。吁亦悲矣。然何必劳君之语迫隘而不公。余尝志己卯录后曰。道与理。万世之所公共也。苟伸于万世之后。生于万世之前者。与有幸焉。
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侯欲为帝也。楷说近理。然余以为黄河数千年而或清。盖喻升平之难见。非以河清为升平之兆也。京房未晓而傅会易传也。昔人咏河清诗曰。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河清之兆应且无论。诗人之意。吁亦悲矣。然何必劳君之语迫隘而不公。余尝志己卯录后曰。道与理。万世之所公共也。苟伸于万世之后。生于万世之前者。与有幸焉。或问余曰。子亦有所恶乎。曰有之。胡广,冯道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