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x 页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杂著
杂著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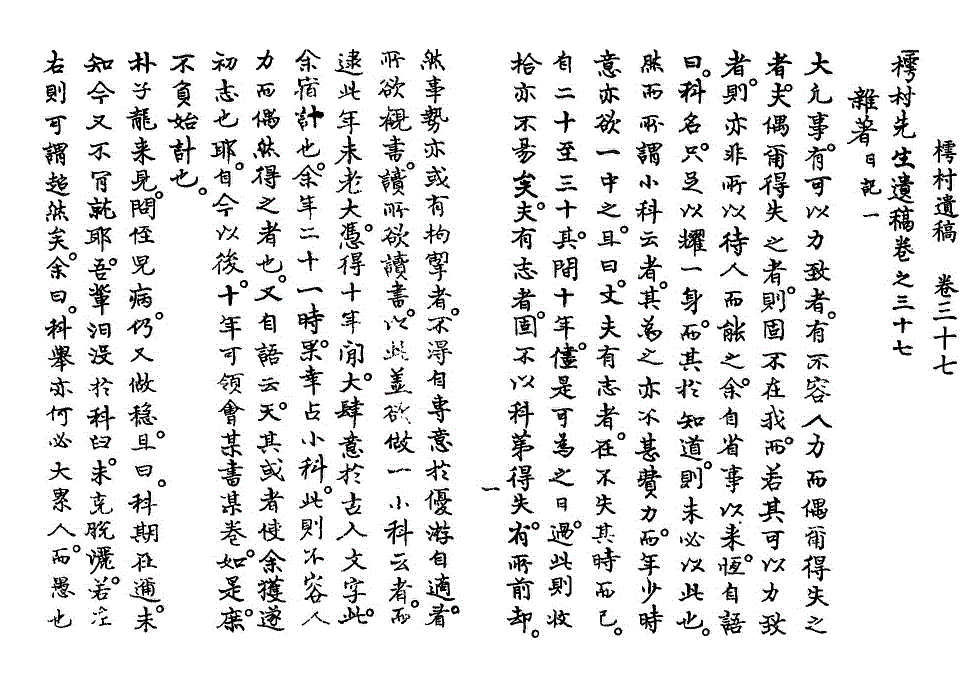 日记(一)
日记(一)大凡事。有可以力致者。有不容人力而偶尔得失之者。夫偶尔得失之者。则固不在我。而若其可以力致者。则亦非所以待人而能之。余自省事以来。恒自语曰。科名。只足以耀一身。而其于知道。则未必以此也。然而所谓小科云者。其为之亦不甚费力。而年少时意亦欲一中之。且曰。丈夫有志者。在不失其时而已。自二十至三十。其间十年。尽是可为之日。过此则收拾亦不易矣。夫有志者。固不以科第得失。有所前却。然事势亦或有拘掣者。不得自专意于优游自适。看所欲观书。读所欲读书。以此盖欲做一小科云者。而逮此年未老大。凭得十年閒。大肆意于古人文字。此余宿计也。余年二十一时。果幸占小科。此则不容人力而偶然得之者也。又自语云。天其或者使余获遂初志也耶。自今以后。十年可领会某书某卷。如是。庶不负始计也。
朴子龙来见。问侄儿病。仍又做稳。且曰。科期在迩。未知今又不肯就耶。吾辈汨没于科臼。未克脱洒。若左右则可谓超然矣。余曰。科举亦何必大累人。而愚也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2L 页
 性本懒散。不能以时加工。如是且阅五六岁。今虽勉策驽钝。实无以趁时限捏撰文字。以自试焉。今科则稍俟病忧少间。欲就人做得若干篇而赴举计。而然而得失。则吾之器既不能如人之利。已置之度外矣。子龙曰。吾尝闻左右事多矣。今适从容。可良晤矣。大抵为人之道。既有第一义。学问是也。吾辈既入于舁彀中。此事为吾兄。更勉之。或奖或戒。甚缕缕。余闻其言。而中窃瞿然。子龙早从其家庭。得闻训迪之方。而为人清亮可喜。今为吾勉戒之者如是者。必其所闻于人者过矣。然朋友之责励之者。既如此。则愚也自修之道。益不可不加意。而颓散自适。易就退转。怛然自惧。愧无以副朋侪之望也。(十九日。)
性本懒散。不能以时加工。如是且阅五六岁。今虽勉策驽钝。实无以趁时限捏撰文字。以自试焉。今科则稍俟病忧少间。欲就人做得若干篇而赴举计。而然而得失。则吾之器既不能如人之利。已置之度外矣。子龙曰。吾尝闻左右事多矣。今适从容。可良晤矣。大抵为人之道。既有第一义。学问是也。吾辈既入于舁彀中。此事为吾兄。更勉之。或奖或戒。甚缕缕。余闻其言。而中窃瞿然。子龙早从其家庭。得闻训迪之方。而为人清亮可喜。今为吾勉戒之者如是者。必其所闻于人者过矣。然朋友之责励之者。既如此。则愚也自修之道。益不可不加意。而颓散自适。易就退转。怛然自惧。愧无以副朋侪之望也。(十九日。)三月二十五日。余自孩童时。虽与群儿戏剧。而未尝出门外作遨游也。以是近都门数里许。溪山之可以游览者。举未曾一至焉。则若三角之在十有馀里。而且有登临之劳者。宜其至今日不见矣。近日来朝议以北汉为可城。城既筑矣。又置行宫一所。而至若僧舍之类亦多刱立。要作异日得力之地云矣。都下士大夫争相往观。不翅骏奔。余亦欲一往视其果如何。而朴友子中适来要余以行。以廿有五日有约。余果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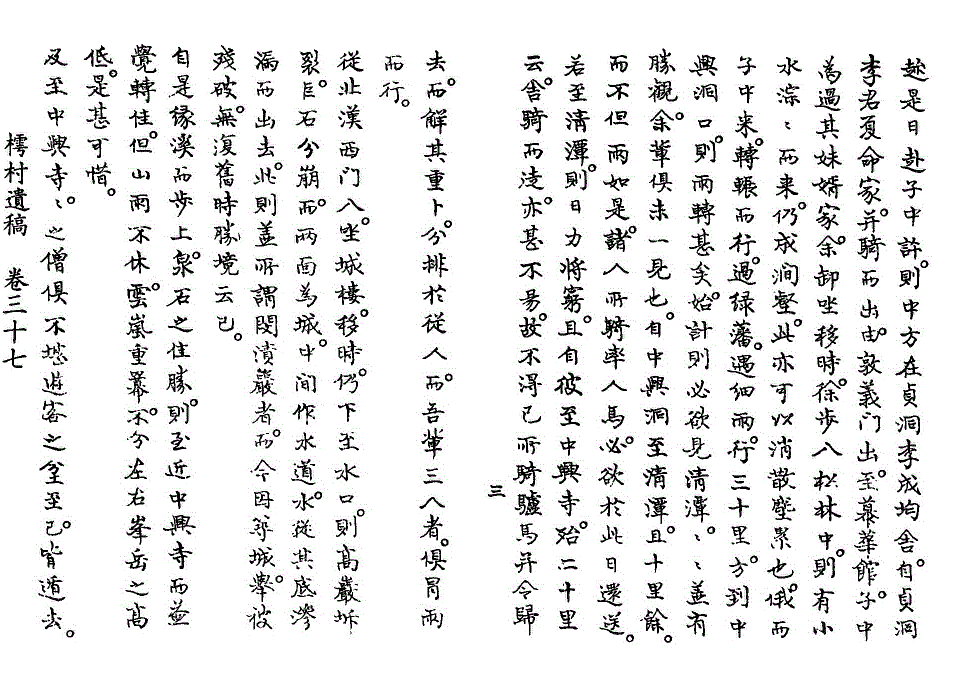 趁是日赴子中许。则中方在贞洞李成均舍。自贞洞李君夏命家。并骑而出。由敦义门出。至慕华馆。子中为过其妹婿家。余卸坐移时。徐步入松林中。则有小水淙淙而来。仍成涧壑。此亦可以消散尘累也。俄而子中来。转辗而行。过绿藩。遇细雨。行三十里。方到中兴洞口。则雨转甚矣。始计则必欲见清潭。清潭盖有胜观。余辈俱未一见也。自中兴洞至清潭。且十里馀。而不但雨如是。诸人所骑率人马。必欲于此日还送。若至清潭。则日力将穷。且自彼至中兴寺。殆二十里云。舍骑而徒。亦甚不易。故不得已所骑驴马并令归去。而解其重卜。分排于从人。而吾辈三人者。俱冒雨而行。
趁是日赴子中许。则中方在贞洞李成均舍。自贞洞李君夏命家。并骑而出。由敦义门出。至慕华馆。子中为过其妹婿家。余卸坐移时。徐步入松林中。则有小水淙淙而来。仍成涧壑。此亦可以消散尘累也。俄而子中来。转辗而行。过绿藩。遇细雨。行三十里。方到中兴洞口。则雨转甚矣。始计则必欲见清潭。清潭盖有胜观。余辈俱未一见也。自中兴洞至清潭。且十里馀。而不但雨如是。诸人所骑率人马。必欲于此日还送。若至清潭。则日力将穷。且自彼至中兴寺。殆二十里云。舍骑而徒。亦甚不易。故不得已所骑驴马并令归去。而解其重卜。分排于从人。而吾辈三人者。俱冒雨而行。从北汉西门入。坐城楼。移时。仍下至水口。则高岩坼裂。巨石分崩。而两面为城。中间作水道。水从其底渗漏而出去。此则盖所谓闵渍岩者。而今因筑城。举被残破。无复旧时胜境云已。
自是缘溪而步上。泉石之佳胜。则至近中兴寺而益觉转佳。但山雨不休。云岚重羃。不分左右峰岳之高低。是甚可惜。
及至中兴寺。寺之僧俱不堪游客之坌至。已皆遁去。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3L 页
 而役丁数十辈。以僧舍为其寄宿之所。窗牗破缺。房奥圮倾。且无床席之可坐矣。
而役丁数十辈。以僧舍为其寄宿之所。窗牗破缺。房奥圮倾。且无床席之可坐矣。而若至山堂。则可得就煖燎衣。下榻稳眠矣。不道陋劣之若此也。仍倩人作饭。亦得以充饥。至夜则各以身比卧而宿。
翌朝起。看天宇。犹不收霁而云阴重驳。烟雾四遮。左右诸山虽对只尺。而犹未得其真面也。但川流激石澎湃之声。自令人便起遐想也。诸人相语曰。昨日之辛苦。已不须言。而今朝又如此。吾辈之卜日。可谓不善矣。今日又将留滞。而凡百殊多可念。仍令从人取饭而来。及饭已。忽有风声自远而来。山之宿雾重烟。驱驰而糜散。须臾而峰峦俱见。天日明槩。不复如向时之阴翳蒸郁也。余顾语两人曰。此可谓披云雾睹青天。还胜于初不雨阴时也。天之所以饷吾辈游览之乐者。讵不已快畅哉。
仍又出寺而行。转向文殊。整步缓行。历见殿宇新建之处。周旋久之。转辗而去。至西门上所谓▣▣峰者。峰之高虽不及白云台远甚。而犹与普玄诸峰。相上下。眼界甚通快。凭览百里许山海。但以是日有雾气。纵不能穷瞩。而然犹俯视江海。旁压群山。已多雄远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4H 页
 之意。而都城十馀里地。如近在几案间。而宫阙之大。闾廛之盛。一举目而尽得之。甚壮观也。烟云浮遮于半天。而下有十丈埃𡏖。覆盖亿兆人家。就中车马来往。轩貂周章。凡彼荣达忧辱。举皆不入于心中。而令人便起腾空之思。直欲超玄虚接鸿濛。而神游于八弦之外也。
之意。而都城十馀里地。如近在几案间。而宫阙之大。闾廛之盛。一举目而尽得之。甚壮观也。烟云浮遮于半天。而下有十丈埃𡏖。覆盖亿兆人家。就中车马来往。轩貂周章。凡彼荣达忧辱。举皆不入于心中。而令人便起腾空之思。直欲超玄虚接鸿濛。而神游于八弦之外也。仍从西南门出。访入文殊寺。寺之僧两三辈出见见人。亦不甚有难色。比中兴则僧品相远也。寺有窟。颇深僻。有石佛坐其中。左右列立罗汉。不记其数。中有井水。常不渴。居僧饮之。以为泉云。
自文殊午饭后。转下从洞溪而行。十步。而或坐或行。行颇远。殆近平地。而洞益邃。泉石益清胜。自是以往。转步尤入胜境。高岩陡绝。叠石牢落。松老石奇。殆千万状。不道是间忽有如许地也。余谓同行曰。古人常恨桃源之不得更寻为恨。而顾此一重山。宜其浅狭无有藏回之处。而然犹此地。则人迹亦罕到。游人之题名。若干在于石面。而比于中兴洞。则不翅相万矣。盖以其溪路绝险。不可以骑行。虽徒步。必是便捷善行者方到矣。如是故都下游赏者。亦或有不知者。虽余辈偶从溪径而下。仍忽到此。不然则亦将如他人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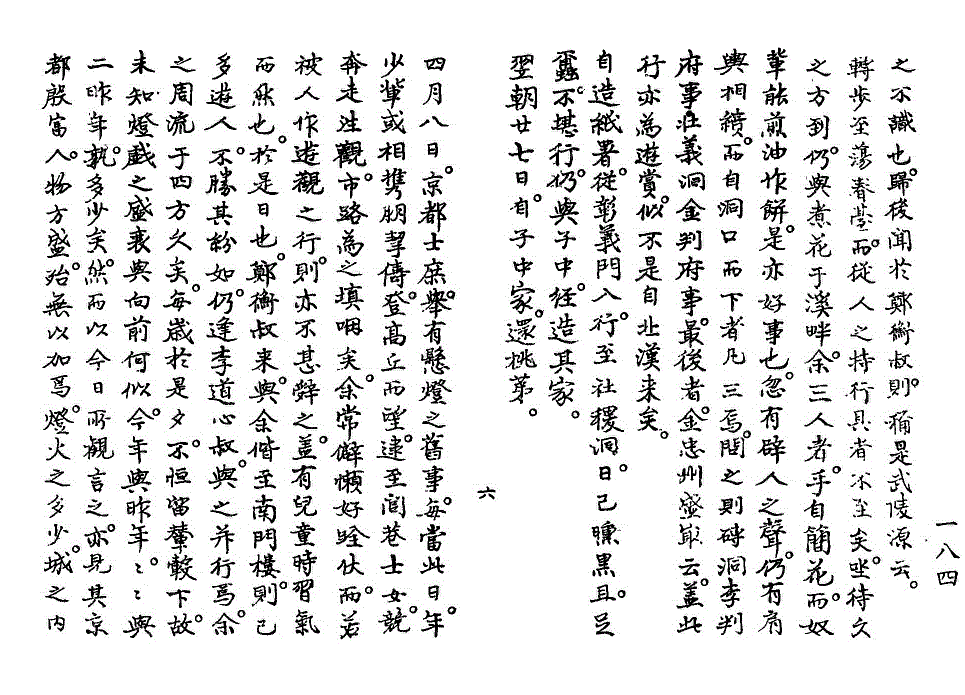 之不识也。归后闻于郑衡叔。则称是武陵源云。
之不识也。归后闻于郑衡叔。则称是武陵源云。转步至荡春台。而从人之持行具者不至矣。坐待久之方到。仍与煮花于溪畔。余三人者。手自简花。而奴辈能煎油作饼。是亦好事也。忽有辟人之声。仍有肩舆相续。而自洞口而下者凡三焉。问之则砖洞李判府事,壮义洞金判府事。最后者。金忠州盛最云。盖此行亦为游赏。似不是自北汉来矣。
自造纸署。从彰义门入。行至社稷洞。日已曛黑。且足茧。不堪行。仍与子中。经造其家。
翌朝廿七日。自子中家。还桃第。
四月八日。京都士庶。举有悬灯之旧事。每当此日。年少辈或相携朋挈俦。登高丘而望。逮至闾巷士女。竞奔走往观。市路为之填咽矣。余常僻懒好跧伏。而若被人作游观之行。则亦不甚辞之。盖有儿童时习气而然也。于是日也。郑衡叔来。与余偕至南门楼。则已多游人。不胜其纷如。仍逢李道心叔。与之并行焉。余之周流于四方久矣。每岁于是夕。不恒留辇毂下。故未知灯戏之盛衰与向前何似。今年与昨年。昨年与二昨年。孰多少矣。然而以今日所观言之。亦见其京都殷富。人物方盛。殆无以加焉。灯火之多少。城之内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5H 页
 外相悬。自昔而然。自贞陵洞迤至六曹为尤盛。盖此间则皆闾阎扑地。家家竞美斗华以玩赏之。或不及人。为可耻矣。且其屋子不广大。而相比而立。又无遮障可碍远眺。故能如是之壮瞩也。三门外。例不逮城中。今岁则不多让焉。自南楼转步至牛首台展望。则自桃芹之洞。至敦义门以外。举皆炫煌夺人目。而水鼓处处以相乐也。盖盛世之荣观。令人有生逢太平之乐矣。猗欤休哉。已而与道心叔分路。余与衡叔。从牛台至旗干旧址。方夜而归。
外相悬。自昔而然。自贞陵洞迤至六曹为尤盛。盖此间则皆闾阎扑地。家家竞美斗华以玩赏之。或不及人。为可耻矣。且其屋子不广大。而相比而立。又无遮障可碍远眺。故能如是之壮瞩也。三门外。例不逮城中。今岁则不多让焉。自南楼转步至牛首台展望。则自桃芹之洞。至敦义门以外。举皆炫煌夺人目。而水鼓处处以相乐也。盖盛世之荣观。令人有生逢太平之乐矣。猗欤休哉。已而与道心叔分路。余与衡叔。从牛台至旗干旧址。方夜而归。十一日。余有事于楸下。尹友仲和。亦往其山所。坡州与长湍。只争半日之程。而湍之路。必由于坡。余乃与仲和约与之行。离京有先后。追至碧蹄而始相遇。仍与语及山所。凡百排置等事。仲和曰。吾家之墓于长湍。其来久矣。自丽季而已然。至吾曾祖公。营置墓下田几许顷。又有僮仆五家口以守之曰。余看人家。各因其子孙之贫富贵贱。而先墓享祀之节及守护之事。有所礼薄勤歇也。此虽其子孙向先之情。固无彼此。而顾其力之能不能。自不得不如是也。余今以田几顷奴几人。为墓位除出。此则不问其多少增损。为余子孙者。不可有所分持自私也。当其节祀时及凡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5L 页
 有山所修护之役。则举皆出力完了。不宜各自异同也。当初立教既如是。故子孙不敢歧议。而至今遵守以行。今则墓下奴仆。殆至五十馀口。田亩之所出。子孙亦不染指。只于节日。则饼饭等物。皆自此而出。其他则不问云云。此法尽可行。如能有力可以及此。则此足取以为法。故姑识之。
有山所修护之役。则举皆出力完了。不宜各自异同也。当初立教既如是。故子孙不敢歧议。而至今遵守以行。今则墓下奴仆。殆至五十馀口。田亩之所出。子孙亦不染指。只于节日。则饼饭等物。皆自此而出。其他则不问云云。此法尽可行。如能有力可以及此。则此足取以为法。故姑识之。六月五日。余曾于坡州归路。历入清潭。适其时。潭之主人奉板舆而至。余不得进。逡巡于洞口。及其去后。虽得一寄目。而恨未遍焉。其后季夏之五日。余陪家庭及伯父主。他人则李副率,李直长,李丈日进君养,尹直长伯修。同约而行。是日有雨。忽阴忽晴。各披雨衣而行至清潭。则伯修甫已倩于其主人。得其亭榭之开锁铁。仍洞排窗牗。倚槛坐啸。已觉清趣之十分矣。亭不过五六架。而结搆甚精。面势亦颇得宜。西有峭壁高可八九丈。有杂树荟蔚。其下则即清流转石激泻而下。旧有潭。今为沙砾填委。水仍浅而不成潭。犹以清潭见称者。盖以此云。亭前有盘石。广可坐许多人。其下一层。又有平铺可盘桓之石。而有柳老。仍偃卧溪上。乃据柳而坐。垂脚于溪流。濯足幽吟。甚适意也。亭东有桥。可往来人。桥之东。有精舍。为优婆塞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6H 页
 所止宿。得地甚高。自亭子仰见之。则亦觉其幽郁隐映。又助一胜矣。清潭之名。显于今。而好之者有或以为无此俪。李都正晚成甫至曰。吾一生有山水癖。卒未直其地。今见此区。则尽知七十年虚生也云。亭之主人席猗顿之资。遇会心处。一举手。辄办成。盖不甚费力。玆亭虽刱置。凡其妆点。则未尽遍。此后六七年后来观之。则必又有尤胜者矣。作午饭后。仍下来。从延曙路。晡时方还桃第。
所止宿。得地甚高。自亭子仰见之。则亦觉其幽郁隐映。又助一胜矣。清潭之名。显于今。而好之者有或以为无此俪。李都正晚成甫至曰。吾一生有山水癖。卒未直其地。今见此区。则尽知七十年虚生也云。亭之主人席猗顿之资。遇会心处。一举手。辄办成。盖不甚费力。玆亭虽刱置。凡其妆点。则未尽遍。此后六七年后来观之。则必又有尤胜者矣。作午饭后。仍下来。从延曙路。晡时方还桃第。壬辰四月不记日。遂如自德寺。来访余于桃溪。此师与余识面。且十年。始遇于连山之新孤云。其后余家还于洛。师亦浮游至龙门山。仍又盘礴不去。见今在德寺云。师之道未知果何如。而其能解文字晓梵书。不比寻常缁流也。故余许其往来。而不辞之也。此来亦与之叙话。良久。且曰。儒家之所谓理学。吾不能知之。果如何耶。吾之寺有一措大。竟日危坐。未尝见其笑语。拱手对案。亦未知其看书也。食后则时或起行缓步。亦见其捧手舒足。犹恐或有所倾坠而已。坐又复然。未知此乃所谓理学云者耶。问其姓名与所住。则俱不知矣。余闻此窃不胜其警惕。恨未得一识之。以观其如何人也。此人虽似固滞。而初学克己之功。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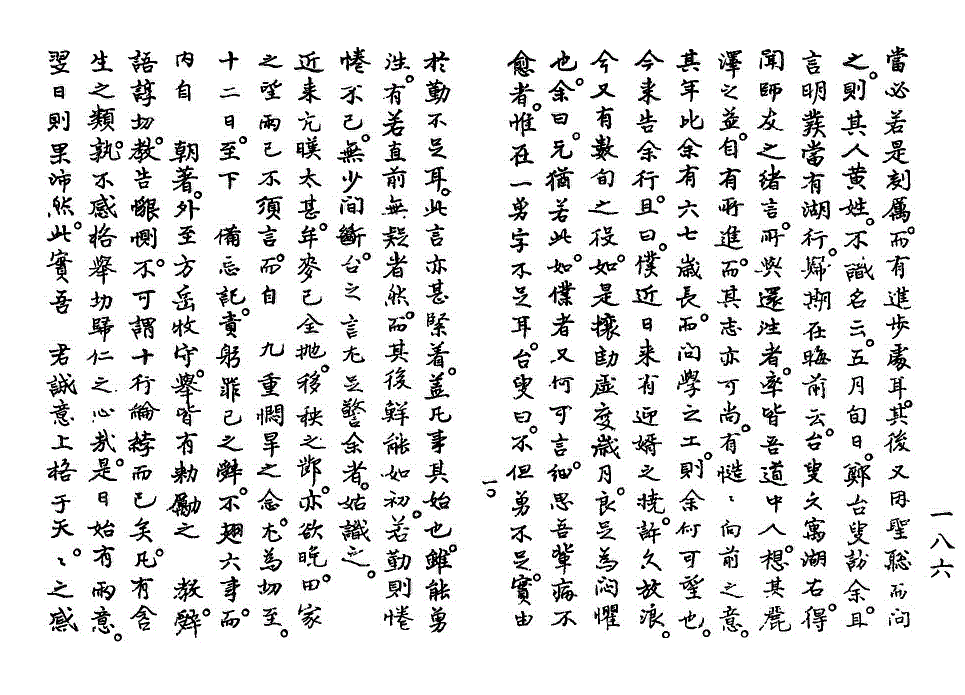 当必若是刻厉。而有进步处耳。其后又因圣聪而问之。则其人黄姓。不识名云。五月旬日。郑台叟访余。且言明发当有湖行。归期在晦前云。台叟久寓湖右。得闻师友之绪言。所与还往者。率皆吾道中人。想其丽泽之益。自有所进。而其志亦可尚。有慥慥向前之意。其年比余有六七岁长。而问学之工。则余何可望也。今来告余行。且曰。仆近日来有迎婿之挠。许久放浪。今又有数旬之役。如是攘劻虚度岁月。良足为闷惧也。余曰。兄犹若此。如仆者又何可言。细思吾辈病不愈者。惟在一勇字不足耳。台叟曰。不但勇不足。实由于勤不足耳。此言亦甚紧着。盖凡事其始也。虽能勇往。有若直前无疑者然。而其后鲜能如初。若勤则惓惓不已。无少间断。台之言尤足警余者。姑识之。
当必若是刻厉。而有进步处耳。其后又因圣聪而问之。则其人黄姓。不识名云。五月旬日。郑台叟访余。且言明发当有湖行。归期在晦前云。台叟久寓湖右。得闻师友之绪言。所与还往者。率皆吾道中人。想其丽泽之益。自有所进。而其志亦可尚。有慥慥向前之意。其年比余有六七岁长。而问学之工。则余何可望也。今来告余行。且曰。仆近日来有迎婿之挠。许久放浪。今又有数旬之役。如是攘劻虚度岁月。良足为闷惧也。余曰。兄犹若此。如仆者又何可言。细思吾辈病不愈者。惟在一勇字不足耳。台叟曰。不但勇不足。实由于勤不足耳。此言亦甚紧着。盖凡事其始也。虽能勇往。有若直前无疑者然。而其后鲜能如初。若勤则惓惓不已。无少间断。台之言尤足警余者。姑识之。近来亢暵太甚。牟麦已全抛。移秧之节。亦欲晚。田家之望雨已不须言。而自 九重悯旱之念。尤为切至。
十二日。至下 备忘记。责躬罪己之辞。不翅六事。而内自 朝著。外至方岳牧守。举皆有敕励之 教。辞语谆切。教告𢢽恻。不可谓十行纶綍而已矣。凡有含生之类。孰不感格举切归仁之心哉。是日始有雨意。翌日则果沛然。此实吾 君诚意上格于天。天之感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7H 页
 应于人。又若是遄且信也。已而有以求言而进言者。有曰克恢包容。犹察其投间抵隙之患。又有以用人不工为言者。此两言者视之若汎然。而究其实。则皆不能打破这偏党二字。奈何。余曰。彼高远之天。犹可以格。而人犹不可以言语诱也。
应于人。又若是遄且信也。已而有以求言而进言者。有曰克恢包容。犹察其投间抵隙之患。又有以用人不工为言者。此两言者视之若汎然。而究其实。则皆不能打破这偏党二字。奈何。余曰。彼高远之天。犹可以格。而人犹不可以言语诱也。名之所以误人久矣。不有其实而徒窃其名者。固不足言。虽或有其实。而不须其有名焉。盖实而名不满则无伤。反是则不免为自欺欺人之归。余尝曰。实过其名为君子。名与实等为恒人。名过其实为小人。夫以末世率多好名之士。故余窃病其然。常思其谨敕近实。不作其矫矫之态矣。昨日偶有一家尊属。谓余曰。而之名誉。或有称道之者。至曰。某也为人不易得。凡于事。亦能解识。求之此世。罕其匹伦云云。余既闻其言。不觉面骍。窃自咎曰。余本一伎俩无用底人也。有何衒价于人。而遽取此名也。向余所谓不免为小人者。且将归余耶。尝以轻儇偷薄。为可戒。自附于愚鲁朴陋之目。而或者反以此为纯谨无妄而然耶。以自知无似。凡于事都不晓达。故不敢遇事论卞明其是非。每其问答之际。多以不知为解。而或者反以此为谦抑自卑。不欲显辉而然耶。余亦人也。岂不知有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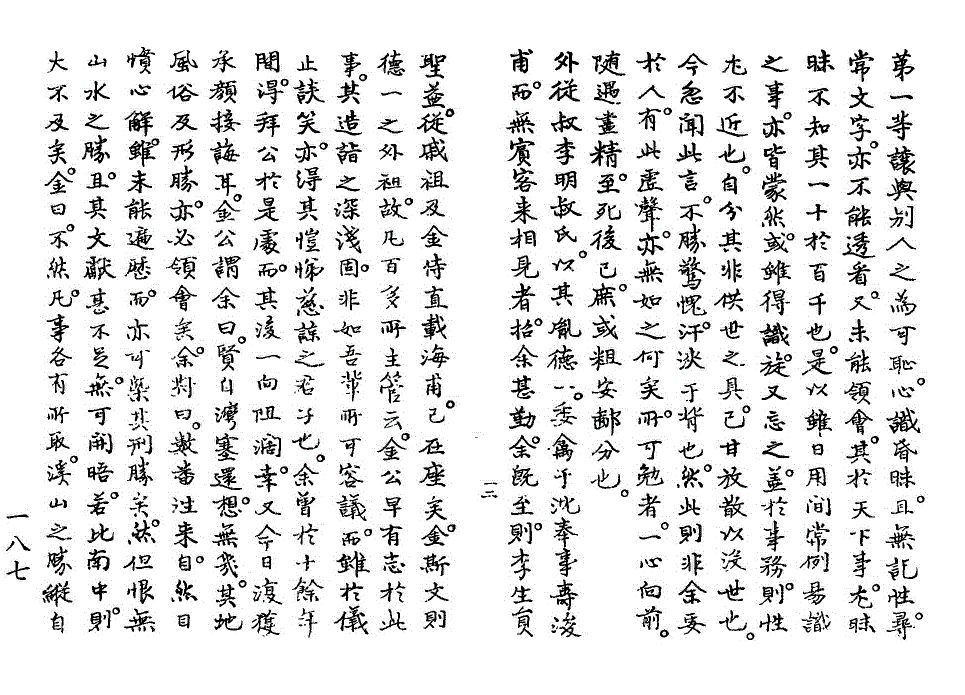 第一等让与别人之为可耻。心识昏昧。且无记性。寻常文字。亦不能透看。又未能领会。其于天下事。尤昧昧不知其一十于百千也。是以虽日用间常例易识之事。亦皆蒙然。或虽得识。旋又忘之。盖于事务。则性尤不近也。自分其非供世之具。已甘放散以没世也。今忽闻此言。不胜惊愧。汗浃于背也。然此则非余要于人。有此虚声。亦无如之何矣。所可勉者。一心向前。随遇尽精。至死后已。庶或粗安鄙分也。
第一等让与别人之为可耻。心识昏昧。且无记性。寻常文字。亦不能透看。又未能领会。其于天下事。尤昧昧不知其一十于百千也。是以虽日用间常例易识之事。亦皆蒙然。或虽得识。旋又忘之。盖于事务。则性尤不近也。自分其非供世之具。已甘放散以没世也。今忽闻此言。不胜惊愧。汗浃于背也。然此则非余要于人。有此虚声。亦无如之何矣。所可勉者。一心向前。随遇尽精。至死后已。庶或粗安鄙分也。外从叔李明叔氏。以其胤德一。委禽于沈奉事寿后甫。而无宾客来相见者。招余甚勤。余既至。则李生员圣益。从戚祖及金侍直载海甫。已在座矣。金斯文则德一之外祖。故凡百多所主管云。金公早有志于此事。其造诣之深浅。固非如吾辈所可容议。而虽于仪止谈笑。亦得其恺悌慈谅之君子也。余曾于十馀年间。得拜公于是处。而其后一向阻阔。幸又今日复获承颜接诲耳。金公谓余曰。贤自湾塞还。想无几。其地风俗及形胜。亦必领会矣。余对曰。数番往来。自然目惯心解。虽未能遍历。而亦可槩其刑胜矣。然但恨无山水之胜。且其文献甚不足。无可开晤。若比南中。则大不及矣。金曰。不然。凡事各有所取。溪山之胜纵自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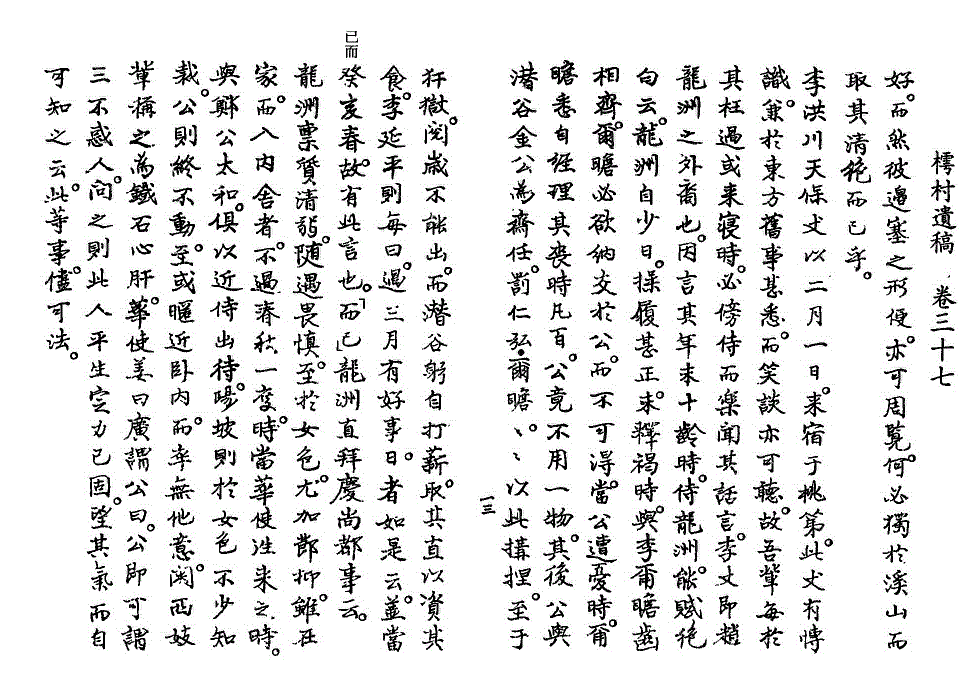 好。而然彼边塞之形便。亦可周览。何必独于溪山而取其清绝而已乎。
好。而然彼边塞之形便。亦可周览。何必独于溪山而取其清绝而已乎。李洪川天保丈以二月一日。来宿于桃第。此丈有博识。兼于东方旧事甚悉。而笑谈亦可听。故吾辈每于其枉过或来寝时。必傍侍而乐闻其话言。李丈即赵龙洲之外裔也。因言其年未十龄时。侍龙洲。能赋绝句云。龙洲自少日。操履甚正。未释褐时。与李尔瞻齿相齐。尔瞻必欲纳交于公。而不可得。当公遭忧时。尔瞻悉自经理其丧时凡百。公竟不用一物。其后公与潜谷金公为斋任。罚仁弘,尔瞻。尔瞻以此搆捏。至于犴狱。阅岁不能出。而潜谷躬自打薪。取其直以资其食。李延平则每曰。过三月有好事。日者如是云。盖当癸亥春。故有此言也。而已(已而)龙洲直拜庆尚都事云。
龙洲禀质清弱。随遇畏慎。至于女色。尤加节抑。虽在家。而入内舍者。不过春秋一度。时当华使往来之时。与郑公太和。俱以近侍出待。阳坡则于女色不少知裁。公则终不动。至或昵近卧内。而卒无他意。关西妓辈称之为铁石心肝。华使姜日广谓公曰。公即可谓三不惑人。问之则此人平生定力已固。望其气而自可知之云。此等事。尽可法。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8L 页
 又曰。龙洲居家。持己甚严。鸡初鸣必晨谒。坐立必以绳墨自程。人未尝见其跛倚。终日无哕气。门人子弟或有困哕者。则必责之以志不胜气。亦不严可云。此于后生。警切甚大。
又曰。龙洲居家。持己甚严。鸡初鸣必晨谒。坐立必以绳墨自程。人未尝见其跛倚。终日无哕气。门人子弟或有困哕者。则必责之以志不胜气。亦不严可云。此于后生。警切甚大。李延阳时白。自少未知名时。已为弼云所重。虽尝不以文学见称。而勤苦笃实。有人所不及者。未达时。尝读书山房。三日读书。则其翌日。必折薪负归。取直于市。以供亲厨。兼以自资其书粮。健而有力。故其一负能敌两牛云。延阳虽勤笃如是。而未曾以文字成名。盖以述著之未见于后而然也。然后生有志者。能以此卖薪资粮之事。存诸中以为警惕。则似不无所益耳。
六月九日。智异山甘露寺僧后贤来。访余于寓所。此僧曾于数月前来见。看其为人。不能清疏可喜。而亦不至甚俗。故余不拒其来矣。今其来。言近往德裕山。转至俗离。仍欲入枫岳。不果而归。且将于再明还其故山云。余谓之曰。看尔不甚凡陋。年亦不甚老大。何尔此往来风埃塌扰之中。失此勉力可为之日耶。僧之道与吾人。本不相似。而凡其用力造次之间。则宜无异也。余既失学。愧年岁之晼晚。固无以警于汝者。而亦欲闻物外有奇魁之材其能刻意力行。以造其道者。有以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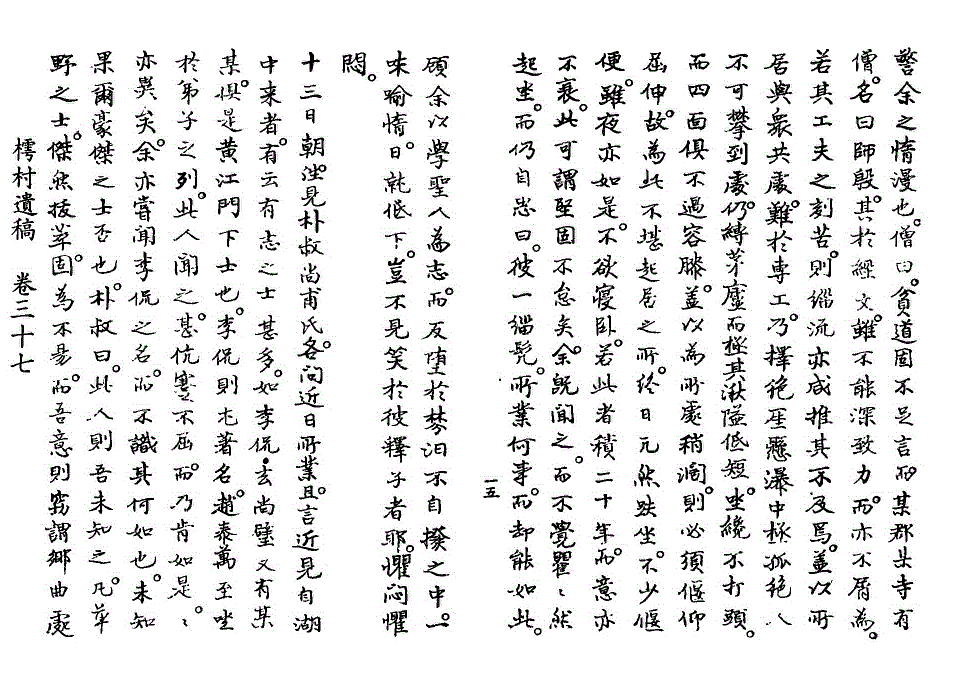 警余之惰漫也。僧曰。贫道固不足言。而某郡某寺有僧。名曰师殷。其于经文。虽不能深致力。而亦不屑为。若其工夫之刻苦。则缁流亦咸推其不及焉。盖以所居与众共处。难于专工。乃择绝厓悬瀑中极孤绝人不可攀到处。仍缚茅庐而极其湫隘低短。坐才不打头。而四面俱不过容膝。盖以为所处稍阔。则必须偃仰屈伸。故为此不堪起居之所。终日兀然趺坐。不少偃便。虽夜亦如是。不欲寝卧。若此者积二十年。而意亦不衰。此可谓坚固不怠矣。余既闻之。而不觉瞿瞿然起坐。而仍自思曰。彼一缁髡。所业何事。而却能如此。顾余以学圣人为志。而反堕于棼汨不自拨之中。一味喻惰。日就低下。岂不见笑于彼释子者耶。惧闷惧闷。
警余之惰漫也。僧曰。贫道固不足言。而某郡某寺有僧。名曰师殷。其于经文。虽不能深致力。而亦不屑为。若其工夫之刻苦。则缁流亦咸推其不及焉。盖以所居与众共处。难于专工。乃择绝厓悬瀑中极孤绝人不可攀到处。仍缚茅庐而极其湫隘低短。坐才不打头。而四面俱不过容膝。盖以为所处稍阔。则必须偃仰屈伸。故为此不堪起居之所。终日兀然趺坐。不少偃便。虽夜亦如是。不欲寝卧。若此者积二十年。而意亦不衰。此可谓坚固不怠矣。余既闻之。而不觉瞿瞿然起坐。而仍自思曰。彼一缁髡。所业何事。而却能如此。顾余以学圣人为志。而反堕于棼汨不自拨之中。一味喻惰。日就低下。岂不见笑于彼释子者耶。惧闷惧闷。十三日朝。往见朴叔尚甫氏。各问近日所业。且言近见自湖中来者。有云有志之士甚多。如李侃,玄尚璧又有某某。俱是黄江门下士也。李侃则尤著名。赵泰万至坐于弟子之列。此人闻之。甚伉蹇不屈。而乃肯如是。是亦异矣。余亦尝闻李侃之名。而不识其何如也。未知果尔豪杰之士否也。朴叔曰。此人则吾未知之。凡草野之士。杰然拔萃。固为不易。而吾意则窃谓乡曲处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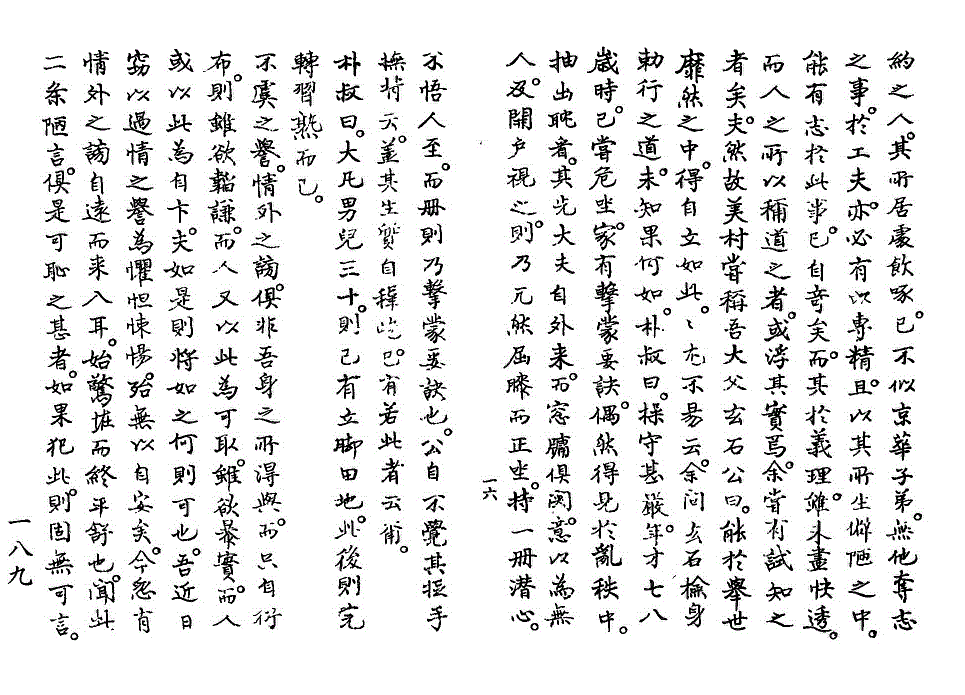 约之人。其所居处饮啄。已不似京华子弟。无他夺志之事。于工夫。亦必有以专精。且以其所生僻陋之中。能有志于此事。已自奇矣。而其于义理。虽未尽快透。而人之所以称道之者。或浮其实焉。余尝有试知之者矣。夫然故美村尝称吾大父玄石公曰。能于举世靡然之中。得自立如此。此尤不易云。余问玄石捡身敕行之道。未知果何如。朴叔曰。操守甚严。年才七八岁时。已尝危坐。家有击蒙要诀。偶然得见于乱秩中。抽出耽看。其先大夫自外来。而窗牗俱关。意以为无人。及开户视之。则乃兀然屈膝而正坐。持一册潜心。不悟人至。而册则乃击蒙要诀也。公自不觉其捉手抚背云。盖其生质自𥠧屹。已有若此者云尔。
约之人。其所居处饮啄。已不似京华子弟。无他夺志之事。于工夫。亦必有以专精。且以其所生僻陋之中。能有志于此事。已自奇矣。而其于义理。虽未尽快透。而人之所以称道之者。或浮其实焉。余尝有试知之者矣。夫然故美村尝称吾大父玄石公曰。能于举世靡然之中。得自立如此。此尤不易云。余问玄石捡身敕行之道。未知果何如。朴叔曰。操守甚严。年才七八岁时。已尝危坐。家有击蒙要诀。偶然得见于乱秩中。抽出耽看。其先大夫自外来。而窗牗俱关。意以为无人。及开户视之。则乃兀然屈膝而正坐。持一册潜心。不悟人至。而册则乃击蒙要诀也。公自不觉其捉手抚背云。盖其生质自𥠧屹。已有若此者云尔。朴叔曰。大凡男儿三十。则已有立脚田地。此后则完转习熟而已。
不虞之誉。情外之谤。俱非吾身之所得与。而只自衍布。则虽欲韬谦。而人又以此为可取。虽欲暴实。而人或以此为自卞。夫如是则将如之何则可也。吾近日窃以过情之誉为惧怛悚惕。殆无以自安矣。今忽有情外之谤自远而来入耳。始惊怪而终平舒也。闻此二条陋言。俱是可耻之甚者。如果犯此。则固无可言。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0H 页
 而若不似人言。则于余。亦奈何哉。然自古有如此而得毁言者亦何限。苟无情分而不识余者。其将何以知不如人之为言耶。此则在人。固不与我。在我者。惟当以此更为戒谨之本。益加修为。积其诚信。则内省固不疚于心。人之为言虽不已。而亦奈何。
而若不似人言。则于余。亦奈何哉。然自古有如此而得毁言者亦何限。苟无情分而不识余者。其将何以知不如人之为言耶。此则在人。固不与我。在我者。惟当以此更为戒谨之本。益加修为。积其诚信。则内省固不疚于心。人之为言虽不已。而亦奈何。凡事之致尤。有或以不能谨行。又有不慎枢机而致。然虽其所失之有大小之可言。而此则固矣。至若近日事。则殊可笑。而或多以此为余言者。余不知其何说也。余本懒散。凡于世俗利害。不能汲汲。而至于科举得失。亦不能如他人焉。今春赴举时。自知无举子工程。以为占取计。而实为吾 伯父主。不敢却步图便也。伊日之剧雨竟日。士子各自庇身不暇。更不容责之以道理也。余之就仲和者。盖亦不得已。而及今之以余在仲和接中。有欲引实其事者。其意抑独何哉。余与其人。本非同事。虽有三数面之雅。而情分既无自别矣。凡士之交道。有不顾身出死力以相济者。而若此以此事。则殊不伦。何也。朋友之间。忽有被身名蔑污。或至于生死之可虑。而非其罪。则为其朋友者。苟有一分可助之道。则惟义之视。不计与之俱颠沛矣。今之事则有不然者。彼此既无契义之厚。虽与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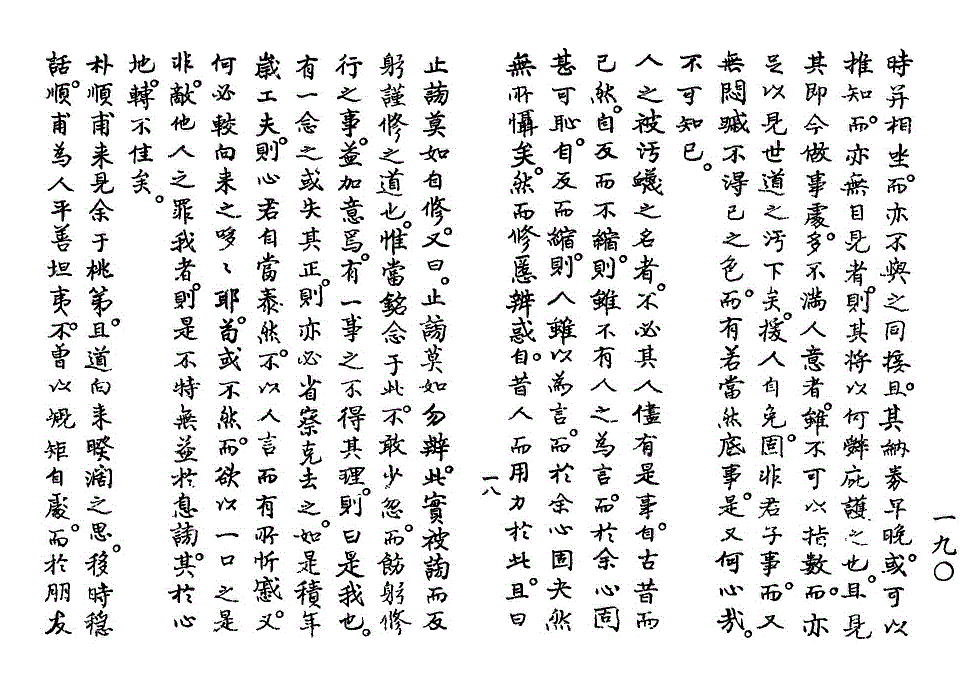 时并相坐。而亦不与之同接。且其纳券早晚。或可以推知。而亦无目见者。则其将以何辞庇护之也。且见其即今做事处。多不满人意者。虽不可以指数。而亦足以见世道之污下矣。援人自免。固非君子事。而又无闷䠞不得已之色。而有若当然底事。是又何心哉。不可知已。
时并相坐。而亦不与之同接。且其纳券早晚。或可以推知。而亦无目见者。则其将以何辞庇护之也。且见其即今做事处。多不满人意者。虽不可以指数。而亦足以见世道之污下矣。援人自免。固非君子事。而又无闷䠞不得已之色。而有若当然底事。是又何心哉。不可知已。人之被污蔑之名者。不必其人尽有是事。自古昔而已然。自反而不缩。则虽不有人之为言。而于余心固甚可耻。自反而缩。则人虽以为言。而于余心固夬然无所慑矣。然而修慝辨惑。自昔人而用力于此。且曰止谤莫如自修。又曰。止谤莫如勿辨。此实被谤而反躬谨修之道也。惟当铭念于此。不敢少忽。而饬躬修行之事。益加意焉。有一事之不得其理。则曰是我也。有一念之或失其正。则亦必省察克去之。如是积年岁工夫。则心君自当泰然。不以人言而有所忻戚。又何必较向来之哆哆耶。苟或不然。而欲以一口之是非。敌他人之罪我者。则是不特无益于息谤。其于心地。转不佳矣。
朴顺甫来见余于桃第。且道向来睽阔之思。移时稳话。顺甫为人平善坦夷。不曾以规矩自处。而于朋友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1H 页
 有诚意。余之所以取于顺甫者如此。而未知顺甫以何事。乐与我游从也。而又曰。向吾有疾且危。自分不复起为人。而目前两童乌稚弱甚可怜。病里犹复以此为念。至呼家人而谓之曰。两儿可念。托余以身后事者。在一家惟有礼敬朋友。则▣▣是其人也。到今思此语。殊觉可笑。而亦可见余仗兄之不浅也。顷见圣初兄。亦尝与之语此云云。愚闻其言。虽感顺甫之待余深。而且惧朋友之责重。将无以副其所期望也。
有诚意。余之所以取于顺甫者如此。而未知顺甫以何事。乐与我游从也。而又曰。向吾有疾且危。自分不复起为人。而目前两童乌稚弱甚可怜。病里犹复以此为念。至呼家人而谓之曰。两儿可念。托余以身后事者。在一家惟有礼敬朋友。则▣▣是其人也。到今思此语。殊觉可笑。而亦可见余仗兄之不浅也。顷见圣初兄。亦尝与之语此云云。愚闻其言。虽感顺甫之待余深。而且惧朋友之责重。将无以副其所期望也。七夕日。在荷坞避暄坐北窗下。方披见吕子约问仁说。而适见丁儿踯躅于阶上。有似捕获之状。余视之。则有蜘蛛结网。而飞虫罥挂于其间。欲去不得。方自转辗而网丝益弥甚可怜也。儿亦见此状。意闷之。欲解其纷。而渠手不及援。盘旋久之。无奈何。乃忽走得一竿竹以来。伫立引之。又不及。余嘉其有恻隐之心。能欲济其急。招而进之。使又得一竿竹。合而缚之使长。仍与于儿。乃大喜踊跃而前。一举而即解之。脱其缠绕而拂拭之。使之飞而去。然后渠意方快适乃已。余见其如此。自不觉其有喜心。若令此儿。推此意而使大之。则亦足于人有所济矣。此虽与孺子入井事异。而若其恻隐之心自发于中。有如此者。则无异同矣。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1L 页
 在桃第。奴星忽报有弊衲欲相见云。使招而进之。乃信和也。余与信和别于清川者。已再阅岁于玆。今忽来访。其意亦勤。而阻阔之馀。得此邂逅。其喜可知也。仍扣其自何来而见今所住锡之所。则对以自宝盖山转到。而向来栖止。则多在太白云云。和之容状。本自颀然好丈夫也。而年来自薄其躬甚矣。一缊袍已十年。不改以备冬夏。一于饭。不必朝夕。具得之。不辞其多。不得则或至并日阙食焉。人之见之甚鄙之。不以昔之所以俟渠者视之。而渠则犹若自得者焉。盖自以为人之所以有屈意。不免作人情者。以其有所求而已。衣与食。既不能自我而取足。则必须于人。夫如是。岂能不有所屈。而人亦得以钳我矣。余既不可遍为而无求于世。则只合作忍冻耐饥底一痴呆汉耳。人之畀予而僇予者。固其宜。而余亦自安而不屑于彼也。余见其皃。已了其非庸众缁流。而又闻其言。益信其为人也。和之警余之语曰。上庠立志犹未确然。更勉之。贫道则已自有得力处。盖虽自嬉。而非可以语言道说也。且曰。古人有云择交。不在僧俗。贫道之于上舍。自以为知己。未知上舍意果何如欤。
在桃第。奴星忽报有弊衲欲相见云。使招而进之。乃信和也。余与信和别于清川者。已再阅岁于玆。今忽来访。其意亦勤。而阻阔之馀。得此邂逅。其喜可知也。仍扣其自何来而见今所住锡之所。则对以自宝盖山转到。而向来栖止。则多在太白云云。和之容状。本自颀然好丈夫也。而年来自薄其躬甚矣。一缊袍已十年。不改以备冬夏。一于饭。不必朝夕。具得之。不辞其多。不得则或至并日阙食焉。人之见之甚鄙之。不以昔之所以俟渠者视之。而渠则犹若自得者焉。盖自以为人之所以有屈意。不免作人情者。以其有所求而已。衣与食。既不能自我而取足。则必须于人。夫如是。岂能不有所屈。而人亦得以钳我矣。余既不可遍为而无求于世。则只合作忍冻耐饥底一痴呆汉耳。人之畀予而僇予者。固其宜。而余亦自安而不屑于彼也。余见其皃。已了其非庸众缁流。而又闻其言。益信其为人也。和之警余之语曰。上庠立志犹未确然。更勉之。贫道则已自有得力处。盖虽自嬉。而非可以语言道说也。且曰。古人有云择交。不在僧俗。贫道之于上舍。自以为知己。未知上舍意果何如欤。高生翼汉。家高山。有文翰。曩在高县时。翼汉以诸生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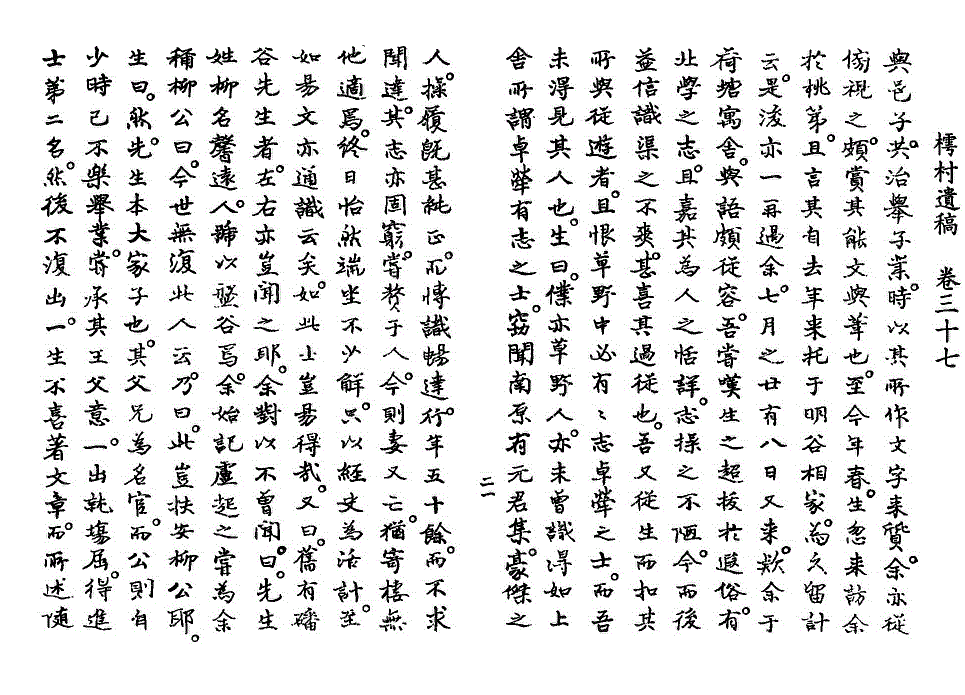 与邑子。共治举子业。时以其所作文字来质。余亦从傍视之。颇赏其能文与笔也。至今年春。生忽来访余于桃第。且言其自去年来托于明谷相家。为久留计云。是后亦一再过余。七月之廿有八日又来。款余于荷塘寓舍。与语颇从容。吾尝叹生之超拔于遐俗。有北学之志。且嘉其为人之恬详。志操之不陋。今而后益信识渠之不爽。甚喜其过从也。吾又从生而扣其所与从游者。且恨草野中必有有志卓荦之士。而吾未得见其人也。生曰。仆亦草野人。亦未曾识得如上舍所谓卓荦有志之士。窃闻南原有元君集。豪杰之人。操履既甚纯正。而博识畅达。行年五十馀。而不求闻达。其志亦固穷。尝赘于人。今则妻又亡。犹寄栖无他适焉。终日怡然端坐不少解。只以经史为活计。至如易文亦通识云矣。如此士岂易得哉。又曰。旧有磻谷先生者。左右亦岂闻之耶。余对以不曾闻。曰。先生姓柳名馨远。人号以盘谷焉。余始记卢起之尝为余称柳公曰。今世无复此人云。乃曰。此岂扶安柳公耶。生曰。然。先生本大家子也。其父兄为名宦。而公则自少时已不乐举业。尝承其王父意。一出就场屈。得进士第二名。然后不复出。一生不喜著文章。而所述随
与邑子。共治举子业。时以其所作文字来质。余亦从傍视之。颇赏其能文与笔也。至今年春。生忽来访余于桃第。且言其自去年来托于明谷相家。为久留计云。是后亦一再过余。七月之廿有八日又来。款余于荷塘寓舍。与语颇从容。吾尝叹生之超拔于遐俗。有北学之志。且嘉其为人之恬详。志操之不陋。今而后益信识渠之不爽。甚喜其过从也。吾又从生而扣其所与从游者。且恨草野中必有有志卓荦之士。而吾未得见其人也。生曰。仆亦草野人。亦未曾识得如上舍所谓卓荦有志之士。窃闻南原有元君集。豪杰之人。操履既甚纯正。而博识畅达。行年五十馀。而不求闻达。其志亦固穷。尝赘于人。今则妻又亡。犹寄栖无他适焉。终日怡然端坐不少解。只以经史为活计。至如易文亦通识云矣。如此士岂易得哉。又曰。旧有磻谷先生者。左右亦岂闻之耶。余对以不曾闻。曰。先生姓柳名馨远。人号以盘谷焉。余始记卢起之尝为余称柳公曰。今世无复此人云。乃曰。此岂扶安柳公耶。生曰。然。先生本大家子也。其父兄为名宦。而公则自少时已不乐举业。尝承其王父意。一出就场屈。得进士第二名。然后不复出。一生不喜著文章。而所述随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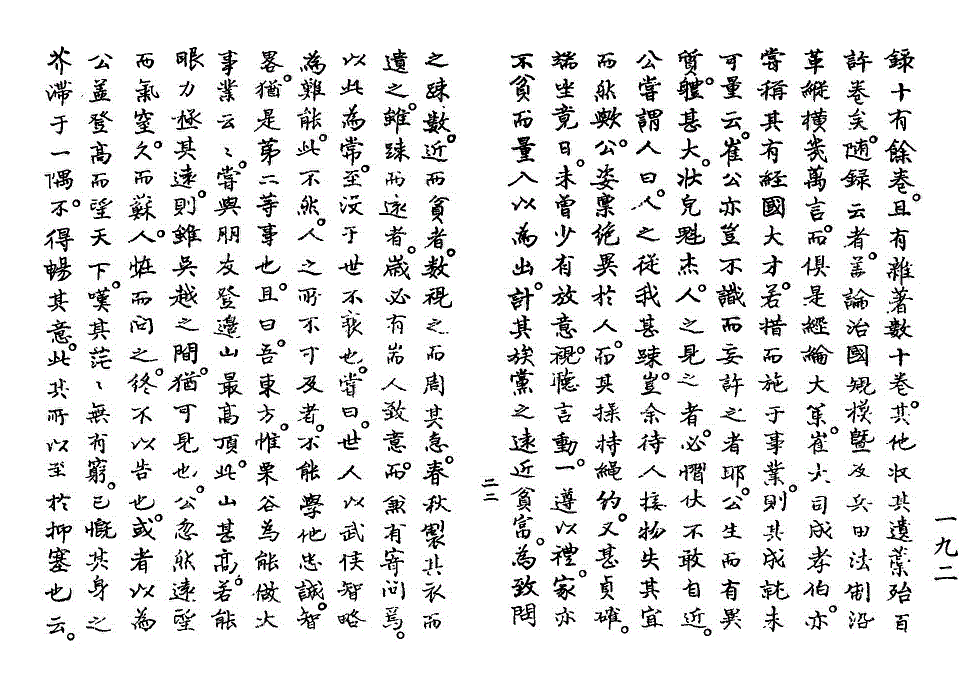 录十有馀卷。且有杂著数十卷。其他收其遗藁殆百许卷矣。随录云者。盖论治国规模暨及兵田法制沿革纵横几万言。而俱是经纶大策。崔大司成孝伯。亦尝称其有经国大才。若措而施于事业。则其成就未可量云。崔公亦岂不识而妄许之者耶。公生而有异质。体甚大。状皃魁杰。人之见之者。必慑伏不敢自近。公尝谓人曰。人之从我甚疏。岂余待人接物失其宜而然欤。公姿禀绝异于人。而其操持绳约。又甚贞确。端坐竟日。未曾少有放意。视听言动。一遵以礼。家亦不贫而量入以为出。计其族党之远近贫富。为致问之疏数。近而贫者。数视之而周其急。春秋制其衣而遗之。虽疏而远者。岁必有耑人致意。而兼有寄问焉。以此为常。至没于世不衰也。尝曰。世人以武侯智略为难能。此不然。人之所不可及者。不能学他忠诚。智略。犹是第二等事也。且曰。吾东方。惟栗谷为能做大事业云云。尝与朋友登边山最高顶。此山甚高。若能眼力极其远。则虽吴越之间。犹可见也。公忽然远望而气窒。久而苏。人怪而问之。终不以告也。或者以为公盖登高而望天下。叹其茫茫无有穷。已慨其身之芥滞于一隅。不得畅其意。此其所以至于抑塞也云。
录十有馀卷。且有杂著数十卷。其他收其遗藁殆百许卷矣。随录云者。盖论治国规模暨及兵田法制沿革纵横几万言。而俱是经纶大策。崔大司成孝伯。亦尝称其有经国大才。若措而施于事业。则其成就未可量云。崔公亦岂不识而妄许之者耶。公生而有异质。体甚大。状皃魁杰。人之见之者。必慑伏不敢自近。公尝谓人曰。人之从我甚疏。岂余待人接物失其宜而然欤。公姿禀绝异于人。而其操持绳约。又甚贞确。端坐竟日。未曾少有放意。视听言动。一遵以礼。家亦不贫而量入以为出。计其族党之远近贫富。为致问之疏数。近而贫者。数视之而周其急。春秋制其衣而遗之。虽疏而远者。岁必有耑人致意。而兼有寄问焉。以此为常。至没于世不衰也。尝曰。世人以武侯智略为难能。此不然。人之所不可及者。不能学他忠诚。智略。犹是第二等事也。且曰。吾东方。惟栗谷为能做大事业云云。尝与朋友登边山最高顶。此山甚高。若能眼力极其远。则虽吴越之间。犹可见也。公忽然远望而气窒。久而苏。人怪而问之。终不以告也。或者以为公盖登高而望天下。叹其茫茫无有穷。已慨其身之芥滞于一隅。不得畅其意。此其所以至于抑塞也云。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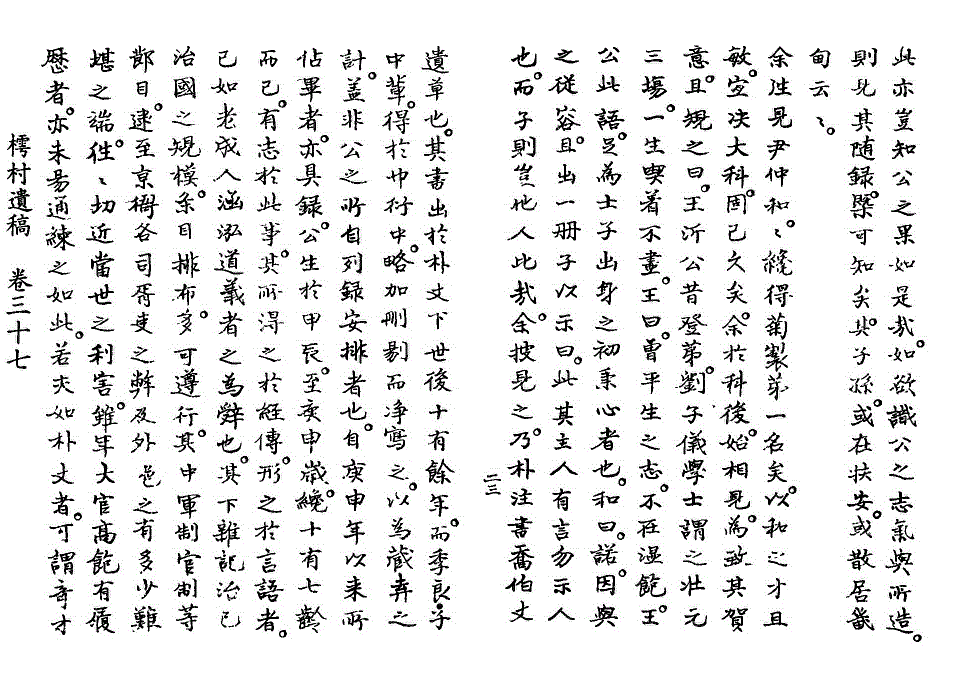 此亦岂知公之果如是哉。如欲识公之志气与所造。则见其随录。槩可知矣。其子孙。或在扶安。或散居畿甸云云。
此亦岂知公之果如是哉。如欲识公之志气与所造。则见其随录。槩可知矣。其子孙。或在扶安。或散居畿甸云云。余往见尹仲和。和才得菊制第一名矣。以和之才且敏。宜决大科。固已久矣。余于科后。始相见。为致其贺意。且规之曰。王沂公昔登第。刘子仪学士谓之壮元三场。一生吃着不尽。王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王公此语。足为士子出身之初秉心者也。和曰。诺。因与之从容。且出一册子以示曰。此其主人有言勿示人也。而子则岂他人比哉。余披见之。乃朴注书乔伯丈遗草也。其书出于朴丈下世后十有馀年。而季良,子中辈。得于巾衍中。略加删剔而净写之。以为藏弆之计。盖非公之所自列录安排者也。自庚申年以来所佔毕者。亦具录。公生于甲辰。至庚申岁。才十有七龄而已。有志于此事。其所得之于经传。形之于言语者。已如老成人涵泓道义者之为辞也。其下杂记治己治国之规模。条目排布。多可遵行。其中军制官制等节目。逮至京衙各司胥吏之弊及外邑之有多少难堪之端。往往切近当世之利害。虽年大官高饱有履历者。亦未易通练之如此。若夫如朴丈者。可谓奇才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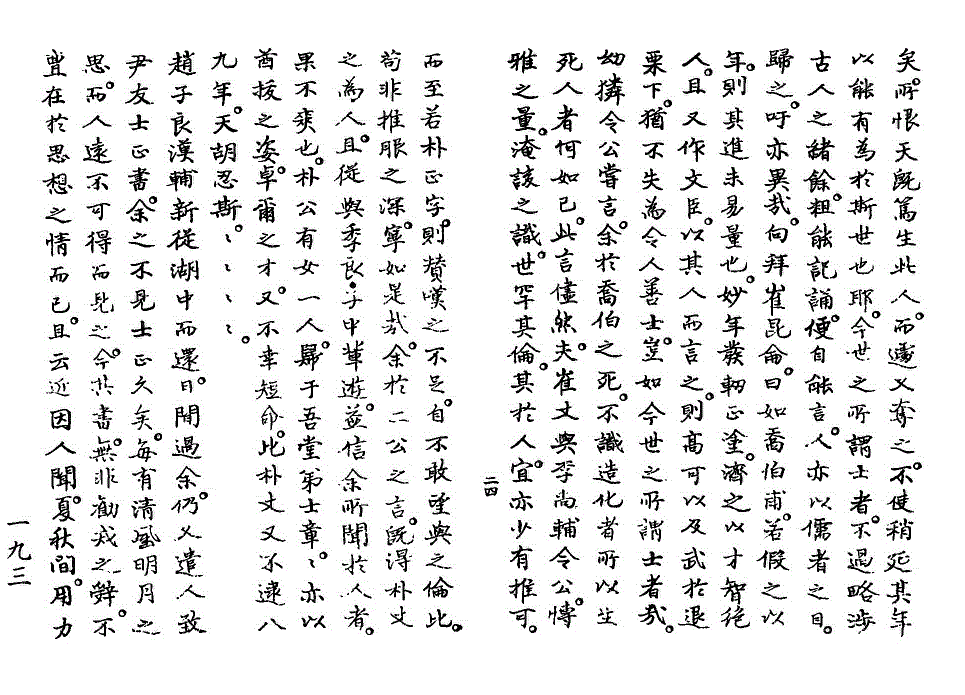 矣。所恨天既笃生此人。而遽又夺之。不使稍延其年以能有为于斯世也耶。今世之所谓士者。不过略涉古人之绪馀。粗能记诵。便自能言。人亦以儒者之目。归之。吁亦异哉。向拜崔昆仑。曰如乔伯甫。若假之以年。则其进未易量也。妙年发轫正涂。济之以才智绝人。且又作文臣。以其人而言之。则高可以及武于退栗下。犹不失为令人善士。岂如今世之所谓士者哉。幼麟令公尝言。余于乔伯之死。不识造化者所以生死人者何如已。此言尽然。夫崔丈与李尚辅令公。博雅之量。淹该之识。世罕其伦。其于人。宜亦少有推可。而至若朴正字。则赞叹之不足。自不敢望与之伦比。苟非推服之深。宁如是哉。余于二公之言。既得朴丈之为人。且从与季良,子中辈游。益信余所闻于人者。果不爽也。朴公有女一人。归于吾堂弟士章。章亦以酋拔之姿。卓尔之才。又不幸短命。比朴丈又不逮八九年。天胡忍斯。天胡忍斯。
矣。所恨天既笃生此人。而遽又夺之。不使稍延其年以能有为于斯世也耶。今世之所谓士者。不过略涉古人之绪馀。粗能记诵。便自能言。人亦以儒者之目。归之。吁亦异哉。向拜崔昆仑。曰如乔伯甫。若假之以年。则其进未易量也。妙年发轫正涂。济之以才智绝人。且又作文臣。以其人而言之。则高可以及武于退栗下。犹不失为令人善士。岂如今世之所谓士者哉。幼麟令公尝言。余于乔伯之死。不识造化者所以生死人者何如已。此言尽然。夫崔丈与李尚辅令公。博雅之量。淹该之识。世罕其伦。其于人。宜亦少有推可。而至若朴正字。则赞叹之不足。自不敢望与之伦比。苟非推服之深。宁如是哉。余于二公之言。既得朴丈之为人。且从与季良,子中辈游。益信余所闻于人者。果不爽也。朴公有女一人。归于吾堂弟士章。章亦以酋拔之姿。卓尔之才。又不幸短命。比朴丈又不逮八九年。天胡忍斯。天胡忍斯。赵子良汉辅新从湖中而还。日间过余。仍又遣人致尹友士正书。余之不见士正久矣。每有清风明月之思。而人远不可得而见之。今其书。无非劝戒之辞。不亶在于思想之情而已。且云近因人闻。夏秋间。用力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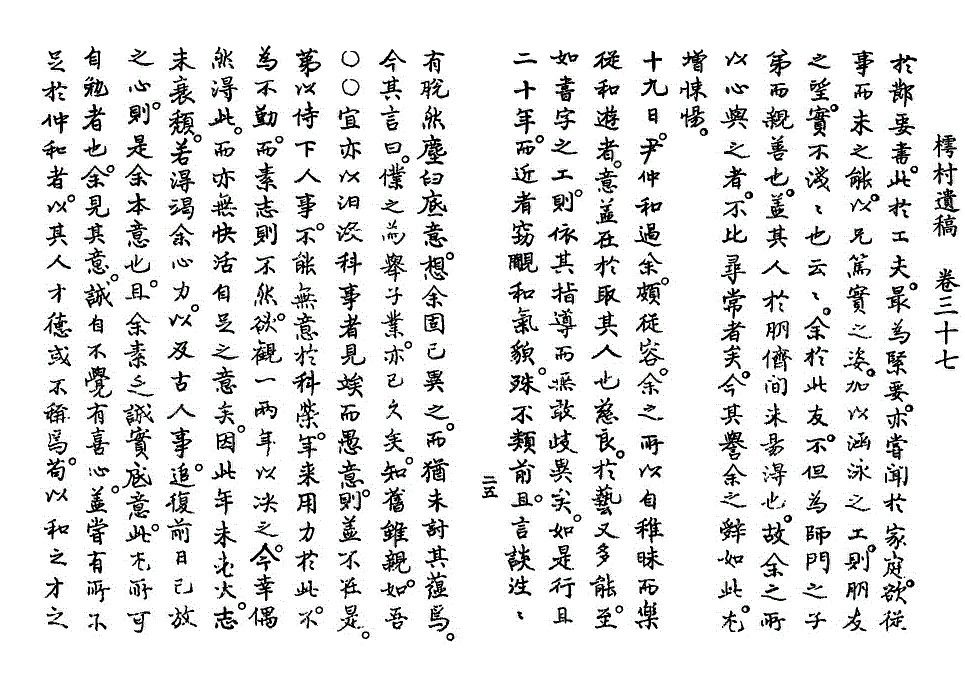 于节要书。此于工夫。最为紧要。亦尝闻于家庭。欲从事而未之能。以兄笃实之姿。加以涵泳之工。则朋友之望。实不浅浅也云云。余于此友。不但为师门之子弟而亲善也。盖其人于朋侪间未易得也。故余之所以心与之者。不比寻常者矣。今其誉余之辞如此。尤增悚惕。
于节要书。此于工夫。最为紧要。亦尝闻于家庭。欲从事而未之能。以兄笃实之姿。加以涵泳之工。则朋友之望。实不浅浅也云云。余于此友。不但为师门之子弟而亲善也。盖其人于朋侪间未易得也。故余之所以心与之者。不比寻常者矣。今其誉余之辞如此。尤增悚惕。十九日。尹仲和过余。颇从容。余之所以自稚昧而乐从和游者。意盖在于取其人也慈良。于艺又多能。至如书字之工。则依其指导而无敢歧异矣。如是行且二十年。而近者窃覸和气貌。殊不类前。且言谈往往有脱然尘臼底意。想余固已异之。而犹未讨其蕴焉。今其言曰。仆之为举子业。亦已久矣。知旧虽亲。如吾▣▣宜亦以汨没科事者见俟而愚意。则盖不在是。第以侍下人事。不能无意于科荣。年来用力于此。不为不勤。而素志则不然。欲观一两年以决之。今幸偶然得此。而亦无快活自足之意矣。因此年未老大。志未衰颓。若得竭余心力。以及古人事。追复前日已放之心。则是余本意也。且余素乏诚实底意。此尤所可自勉者也。余见其意。诚自不觉有喜心。盖尝有所不足于仲和者。以其人才德或不称焉。苟以和之才之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4L 页
 美。有意于为己之事。使其立身修辞。一以实悫自持。则其于通晓事理。机警敏达。则亦未易得其伦比矣。余于是。因其语而力勉之。和亦不以余言为不似也。余且曰兄果用力于此事。则仆虽质陋才下。固无足有裨于高明。而犹当效其一得。勿以俗套例语相期也。和亦笑曰。吾于兄有岁寒之期。宁容若斯耶。乃相视一笑而罢。
美。有意于为己之事。使其立身修辞。一以实悫自持。则其于通晓事理。机警敏达。则亦未易得其伦比矣。余于是。因其语而力勉之。和亦不以余言为不似也。余且曰兄果用力于此事。则仆虽质陋才下。固无足有裨于高明。而犹当效其一得。勿以俗套例语相期也。和亦笑曰。吾于兄有岁寒之期。宁容若斯耶。乃相视一笑而罢。仲和又谓余曰。予之侄得鼎。近忽有非常之事。在五六日前早朝未起之际。见此儿整冠带。入候于各房。及其出而退也。亦坐一室泊如也。窃观其动容周旋逶迤徐缓。非复如昨日之得鼎者矣。余与家兄。俱为惊惑。殊不晓其有何意思。遽乃作此状也。于是闻于其同辈。则盖近日忽然有自拔之意。自语以为吾当早晚脱此旧时羁絷耳。及闻此言。方知渠意所在。吾亦不之怪。而勉渠以勿失此好意思。吾尝以此儿无出人之气。今忽如此。讵不异哉。余闻之。诚不胜惊叹焉。夫年稚志弱者。虽或有此意。亦不能突弁旧来习气。每失于因循苟且。而今此人则遽于一夜而顿尔。去古就新。不少迟疑此。不已美哉。但虑夫良心之发。苟不能日日培养之。而或遇外物之牵制。则有不免退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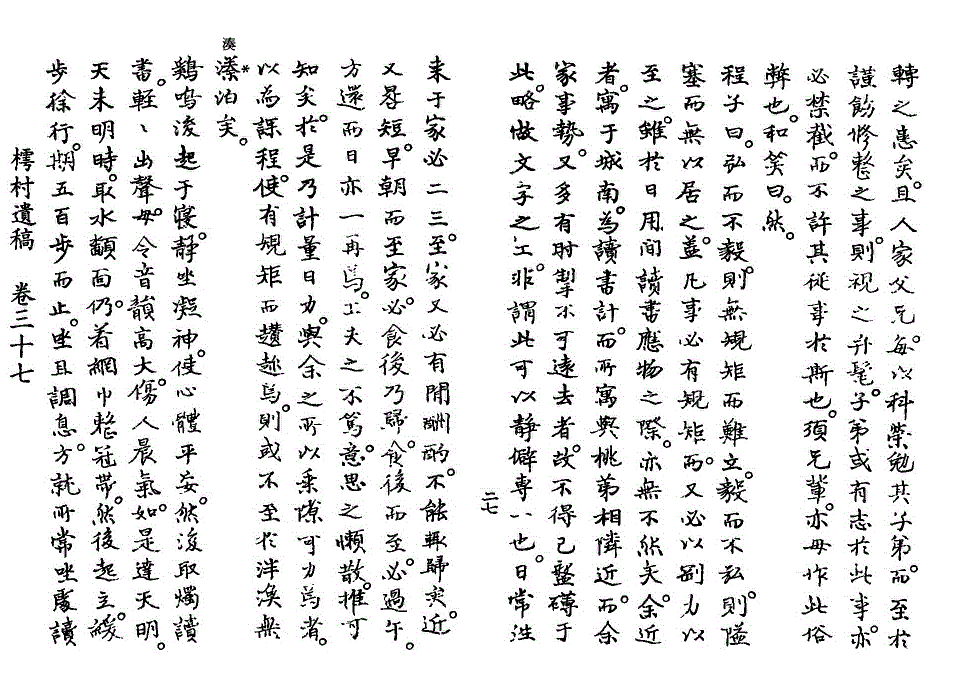 转之患矣。且人家父兄。每以科荣勉其子弟。而至于谨饬修整之事。则视之弁髦。子弟或有志于此事。亦必禁截。而不许其从事于斯也。须兄辈。亦毋作此俗弊也。和笑曰。然。
转之患矣。且人家父兄。每以科荣勉其子弟。而至于谨饬修整之事。则视之弁髦。子弟或有志于此事。亦必禁截。而不许其从事于斯也。须兄辈。亦毋作此俗弊也。和笑曰。然。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塞而无以居之。盖凡事必有规矩。而又必以刚力以至之。虽于日用间读书应物之际。亦无不然矣。余近者。寓于城南。为读书计。而所寓与桃第相邻近。而余家事势。又多有肘掣不可远去者。故不得已盘礴于此。略做文字之工。非谓此可以静僻专一也。日常往来于家必二三。至家又必有閒酬酌。不能辄归矣。近又晷短。早朝而至家。必食后乃归。食后而至。必过午。方还而日亦一再焉。工夫之不笃。意思之懒散。推可知矣。于是乃计量日力。与余之所以乘隙可力焉者。以为课程。使有规矩而趱趁焉。则或不至于泮涣无溱(一作凑)泊矣。
鸡鸣后起于寝。静坐凝神。使心体平妄。然后取烛读书。轻轻出声。毋令音韵高大。伤人晨气。如是达天明。天未明时。取水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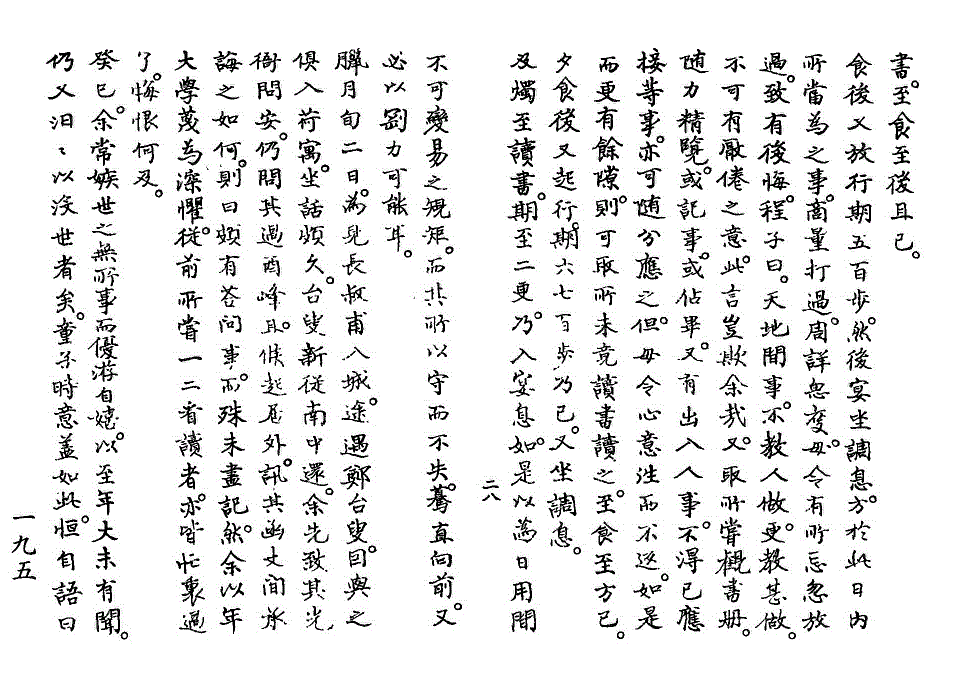 书。至食至后且已。
书。至食至后且已。食后又放行期五百步。然后宴坐调息。方于此日内所当为之事。商量打过。周详思度。毋令有所忘忽放过。致有后悔。程子曰。天地间事。不教人做。更教甚做。不可有厌倦之意。此言岂欺余哉。又取所尝观书册。随力精览。或记事。或佔毕。又有出入人事。不得已应接等事。亦可随分应之。但毋令心意往而不返。如是而更有馀隙。则可取所未竟读书读之。至食至方已。夕食后又起行。期六七百步乃已。又坐调息。
及烛至读书。期至二更。乃入宴息。如是以为日用间不可变易之规矩。而其所以守而不失。蓦直向前。又必以刚力可能耳。
腊月旬二日。为见长叔甫入城。途遇郑台叟。因与之俱入荷寓。坐话颇久。台叟新从南中还。余先致其光衙问安。仍问其过酉峰。且候起居外。讯其函丈间承诲之如何。则曰颇有答问事。而殊未尽记。然余以年大学蔑为深惧。从前所尝一二看读者。亦皆忙里过了。悔恨何及。
癸巳。余常嫉世之无所事而优游自嬉。以至年大未有闻。仍又汨汨以没世者矣。童子时意盖如此。恒自语曰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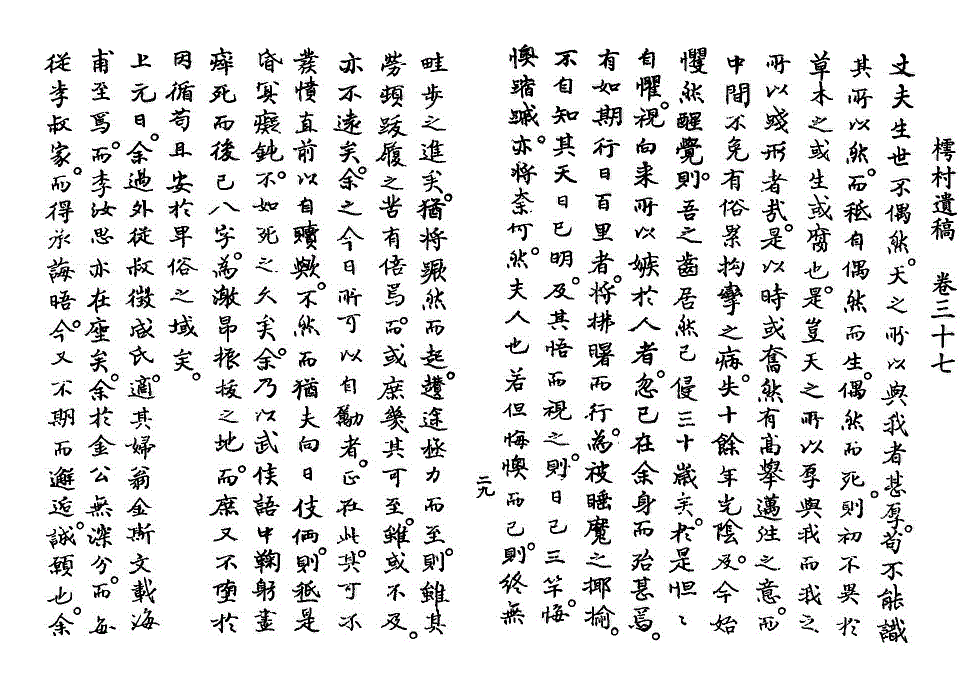 丈夫生世不偶然。天之所以与我者甚厚。苟不能识其所以然。而秪自偶然而生。偶然而死。则初不异于草木之或生或腐也。是岂天之所以厚与我而我之所以践形者哉。是以时或奋然有高举迈往之意。而中间不免有俗累拘挛之病。失十馀年光阴。及今始戄然醒觉。则吾之齿居然已侵三十岁矣。于是怛怛自惧。视向来所以嫉于人者。忽已在余身而殆甚焉。有如期行日百里者。将拂曙而行。为被睡魔之揶揄。不自知其天日已明。及其悟而视之。则日已三竿。悔懊蹜䠞。亦将奈何。然夫人也若但悔懊而已。则终无畦步之进矣。犹将蹶然而起。趱途极力而至。则虽其劳顿跋履之苦有倍焉。而或庶几其可至。虽或不及。亦不远矣。余之今日所可以自励者。正在此。其可不发愤直前以自赎欤。不然而犹夫向日伎俩。则秪是昏冥痴钝。不如死之久矣。余乃以武侯语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字。为激昂振拔之地。而庶又不堕于因循苟且安于卑俗之域矣。
丈夫生世不偶然。天之所以与我者甚厚。苟不能识其所以然。而秪自偶然而生。偶然而死。则初不异于草木之或生或腐也。是岂天之所以厚与我而我之所以践形者哉。是以时或奋然有高举迈往之意。而中间不免有俗累拘挛之病。失十馀年光阴。及今始戄然醒觉。则吾之齿居然已侵三十岁矣。于是怛怛自惧。视向来所以嫉于人者。忽已在余身而殆甚焉。有如期行日百里者。将拂曙而行。为被睡魔之揶揄。不自知其天日已明。及其悟而视之。则日已三竿。悔懊蹜䠞。亦将奈何。然夫人也若但悔懊而已。则终无畦步之进矣。犹将蹶然而起。趱途极力而至。则虽其劳顿跋履之苦有倍焉。而或庶几其可至。虽或不及。亦不远矣。余之今日所可以自励者。正在此。其可不发愤直前以自赎欤。不然而犹夫向日伎俩。则秪是昏冥痴钝。不如死之久矣。余乃以武侯语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字。为激昂振拔之地。而庶又不堕于因循苟且安于卑俗之域矣。上元日。余过外从叔徵咸氏。适其妇翁金斯文载海甫至焉。而李汝思亦在座矣。余于金公无深分。而每从李叔家。而得承诲晤。今又不期而邂逅。诚愿也。余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6L 页
 问汝思于科举去就将如何。思曰。年少于仆者。犹将逡巡。不必问余之有意与否也。金公闻此言。仍讯余于举业不甚努力。曰。士当于科举。去就直截。不宜欲做不做。作依违态。无归宿于彼此耳。诚哉。金公之教余也。余尝自谓歇后人。其于世间事。不欲规规为也。意盖如此。故至如读书修业之事。亦一向懒散弛慢而不加进。所谓举子业者。亦非余卑之不留意也。自少小时。虽从人作文就试。而非其乐。及年大则尤甚。仍又南去数年。全不治业。其间虽一再赴举。而必临时做若干文以入。故率无幸念。亦无甚闷焉。如是优游行且三十岁矣。眷焉惊顾。心窃自语曰。丈夫已三十年读书力行。已失许多时矣。向后若复如斯。则其亦不免支离人也。奈何。潜思厥咎。则盖余歇后二字。卒病余也。余既识病源所由。则其将下所宜药之剂而后病可已。惟振作是良方矣。自今以后。每事当以振作为务。虽彼举业。亦当加意为之。得失则不必横却肚中而已。余于金公之言。有警醒焉。
问汝思于科举去就将如何。思曰。年少于仆者。犹将逡巡。不必问余之有意与否也。金公闻此言。仍讯余于举业不甚努力。曰。士当于科举。去就直截。不宜欲做不做。作依违态。无归宿于彼此耳。诚哉。金公之教余也。余尝自谓歇后人。其于世间事。不欲规规为也。意盖如此。故至如读书修业之事。亦一向懒散弛慢而不加进。所谓举子业者。亦非余卑之不留意也。自少小时。虽从人作文就试。而非其乐。及年大则尤甚。仍又南去数年。全不治业。其间虽一再赴举。而必临时做若干文以入。故率无幸念。亦无甚闷焉。如是优游行且三十岁矣。眷焉惊顾。心窃自语曰。丈夫已三十年读书力行。已失许多时矣。向后若复如斯。则其亦不免支离人也。奈何。潜思厥咎。则盖余歇后二字。卒病余也。余既识病源所由。则其将下所宜药之剂而后病可已。惟振作是良方矣。自今以后。每事当以振作为务。虽彼举业。亦当加意为之。得失则不必横却肚中而已。余于金公之言。有警醒焉。四月。士苟有向前之意。而不欲漫浪以了其身世者。必其愤发勇往底意思多。然后能有所为。而不堕委靡之域矣。不然而才有自私图便之计。有一差过。遽曰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7H 页
 是亦适然。不须每如是而已。有一适意漫散之失。又自恕曰。弛张之道。亦或有此。是岂足妨吾做养之功。而志气又讵可因此有所挠夺也。一之既不能改。而随地每如此。则向之所以知其不可而欲矫之之心。又将忸以为当然底事。不惟不能更其前愆。而日入于浸淫陷下之地。而亦不自知。犹自以谓吾身秪如向日者矣。又窃议其他人之失操就懦者。而不悟其旁观者之又从其后而嗤点而拍手之也。夫人而能刚方不回者。其志固未易走作。而若其柔善和缓者。常失于苟且自欺之患矣。苟能自知其病甚。惕若以改图之。则或可免矣。不若是。则毕竟狼狈。虽欲匍匐而归。亦不可得矣。
是亦适然。不须每如是而已。有一适意漫散之失。又自恕曰。弛张之道。亦或有此。是岂足妨吾做养之功。而志气又讵可因此有所挠夺也。一之既不能改。而随地每如此。则向之所以知其不可而欲矫之之心。又将忸以为当然底事。不惟不能更其前愆。而日入于浸淫陷下之地。而亦不自知。犹自以谓吾身秪如向日者矣。又窃议其他人之失操就懦者。而不悟其旁观者之又从其后而嗤点而拍手之也。夫人而能刚方不回者。其志固未易走作。而若其柔善和缓者。常失于苟且自欺之患矣。苟能自知其病甚。惕若以改图之。则或可免矣。不若是。则毕竟狼狈。虽欲匍匐而归。亦不可得矣。五月三日。午食后至䨥湖崔处士家。崔欣余来。与之欢晤。至日夕方还。盖襄远地。无可与语者。始到闻府之东面。有崔斯文道鸣。有学术文行。而谢举子业。不肯出其庭户。一乡之人。称以为善士。余于是因洛山路。历扣之。其家去州治不满十里。山麓纡回环合。树林亦颇幽胜矣。余遽至。而不带自官家来样子。崔始不觉其何状人。久乃叙话。因及平日向𨓏之情。坐稳移时而回。其后一番约会于洛山。与之联枕。益信其为人。今又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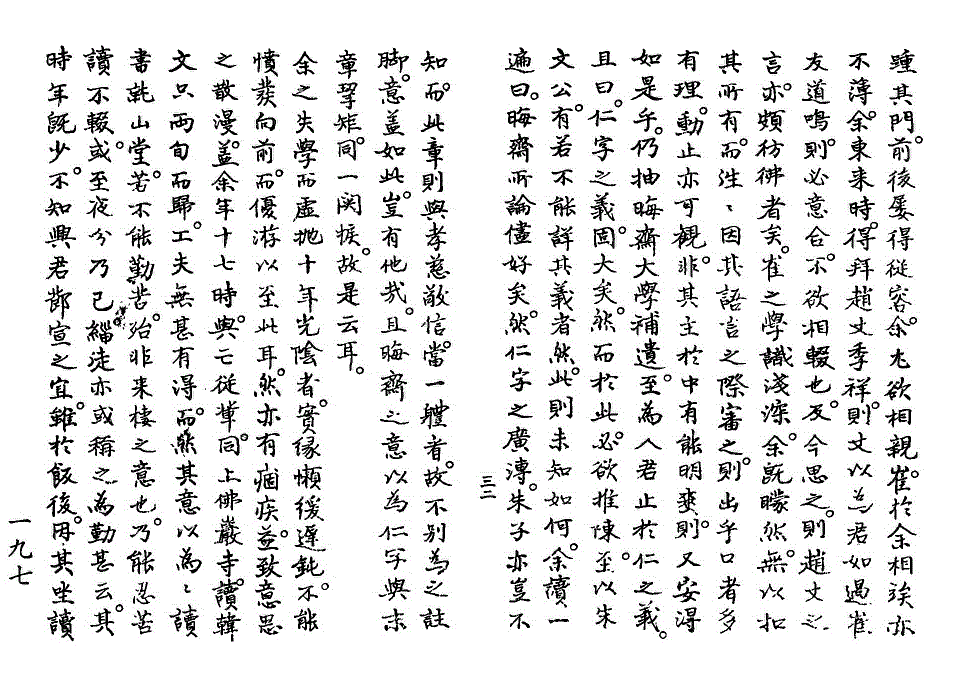 踵其门。前后屡得从容。余尤欲相亲。崔于余相俟亦不薄。余东来时。得拜赵丈季祥。则丈以为君如过崔友道鸣。则必意合。不欲相辍也。及今思之。则赵丈之言。亦颇彷佛者矣。崔之学识浅深。余既矇然。无以扣其所有。而往往因其语言之际审之。则出乎口者多有理。动止亦可观。非其主于中有能明爽。则又安得如是乎。仍抽晦斋大学补遗。至为人君止于仁之义。且曰。仁字之义。固大矣。然而于此。必欲推陈。至以朱文公。有若不能详其义者然。此则未知如何。余读一遍曰。晦斋所论尽好矣。然仁字之广溥。朱子亦岂不知。而此章则与孝慈敬信。当一体看。故不别为之注脚。意盖如此。岂有他哉。且晦斋之意以为仁字与末章挈矩。同一关捩。故是云耳。
踵其门。前后屡得从容。余尤欲相亲。崔于余相俟亦不薄。余东来时。得拜赵丈季祥。则丈以为君如过崔友道鸣。则必意合。不欲相辍也。及今思之。则赵丈之言。亦颇彷佛者矣。崔之学识浅深。余既矇然。无以扣其所有。而往往因其语言之际审之。则出乎口者多有理。动止亦可观。非其主于中有能明爽。则又安得如是乎。仍抽晦斋大学补遗。至为人君止于仁之义。且曰。仁字之义。固大矣。然而于此。必欲推陈。至以朱文公。有若不能详其义者然。此则未知如何。余读一遍曰。晦斋所论尽好矣。然仁字之广溥。朱子亦岂不知。而此章则与孝慈敬信。当一体看。故不别为之注脚。意盖如此。岂有他哉。且晦斋之意以为仁字与末章挈矩。同一关捩。故是云耳。余之失学而虚抛十年光阴者。实缘懒缓迟钝。不能愤发向前。而优游以至此耳。然亦有痼疾。益致意思之散漫。盖余年十七时。与亡从辈。同上佛岩寺。读韩文只两旬而归。工夫无甚有得。而然其意以为为读书就山堂。若不能勤苦。殆非来栖之意也。乃能忍苦读不辍。或至夜分乃已。缁徒亦或称之为勤甚云。其时年既少。不知兴君节宣之宜。虽于饭后。因其坐读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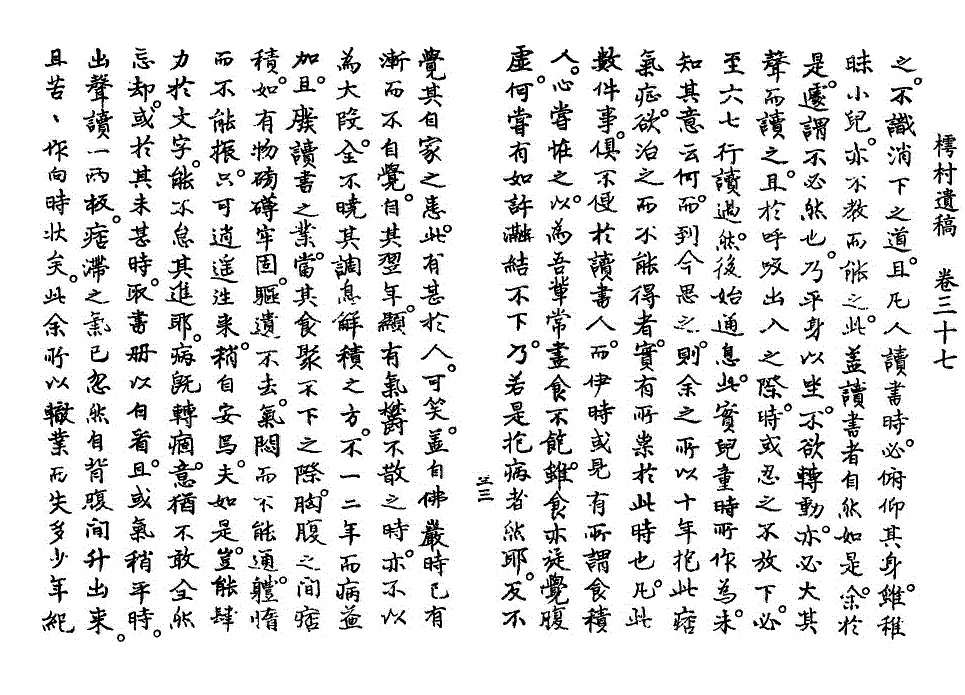 之。不识消下之道。且凡人读书时。必俯仰其身。虽稚昧小儿。亦不教而能之。此盖读书者自然如是。余于是。遽谓不必然也。乃平身以坐。不欲转动。亦必大其声而读之。且于呼吸出入之际。时或忍之不放下。必至六七行读过。然后始通息。此实儿童时所作为。未知其意云何。而到今思之。则余之所以十年抱此痞气症。欲治之而不能得者。实有所祟于此时也。凡此数件事。俱不便于读书人。而伊时或见有所谓食积人。心尝怪之。以为吾辈常尽食不饱。虽食亦旋觉腹虚。何尝有如许瀜结不下。乃若是抱病者然耶。反不觉其自家之患。此有甚于人。可笑。盖自佛岩时已有渐而不自觉。自其翌年。显有气郁不散之时。亦不以为大段。全不晓其调息解积之方。不一二年而病益加。且废读书之业。当其食聚不下之际。胸腹之间痞积。如有物磅礴牢固。驱遗不去。气闷而不能通。体惰而不能振。只可逍遥往来。稍自安焉。夫如是。岂能肆力于文字。能不怠其进耶。病既转痼。意犹不敢全然忘却。或于其未甚时。取书册以自看。且或气稍平时。出声读一两板。痞滞之气已忽然自背腹间升出来。且苦苦作向时状矣。此余所以辙业而失多少年纪
之。不识消下之道。且凡人读书时。必俯仰其身。虽稚昧小儿。亦不教而能之。此盖读书者自然如是。余于是。遽谓不必然也。乃平身以坐。不欲转动。亦必大其声而读之。且于呼吸出入之际。时或忍之不放下。必至六七行读过。然后始通息。此实儿童时所作为。未知其意云何。而到今思之。则余之所以十年抱此痞气症。欲治之而不能得者。实有所祟于此时也。凡此数件事。俱不便于读书人。而伊时或见有所谓食积人。心尝怪之。以为吾辈常尽食不饱。虽食亦旋觉腹虚。何尝有如许瀜结不下。乃若是抱病者然耶。反不觉其自家之患。此有甚于人。可笑。盖自佛岩时已有渐而不自觉。自其翌年。显有气郁不散之时。亦不以为大段。全不晓其调息解积之方。不一二年而病益加。且废读书之业。当其食聚不下之际。胸腹之间痞积。如有物磅礴牢固。驱遗不去。气闷而不能通。体惰而不能振。只可逍遥往来。稍自安焉。夫如是。岂能肆力于文字。能不怠其进耶。病既转痼。意犹不敢全然忘却。或于其未甚时。取书册以自看。且或气稍平时。出声读一两板。痞滞之气已忽然自背腹间升出来。且苦苦作向时状矣。此余所以辙业而失多少年纪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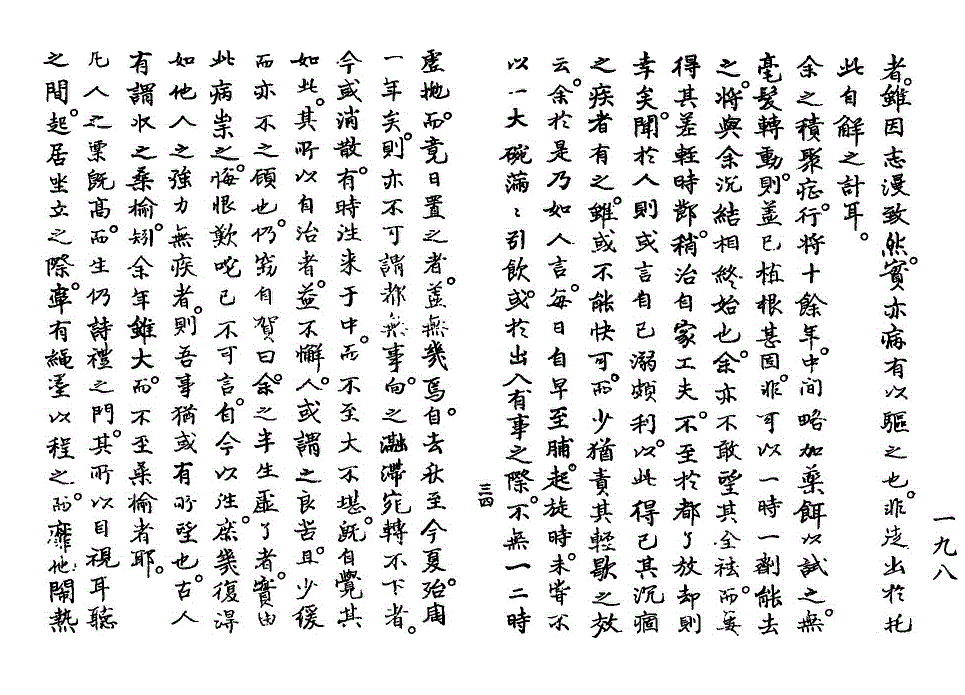 者。虽因志漫致然。实亦病有以驱之也。非徒出于托此自解之计耳。
者。虽因志漫致然。实亦病有以驱之也。非徒出于托此自解之计耳。余之积聚症。行将十馀年。中间略加药饵以试之。无毫发转动。则盖已植根甚固。非可以一时一剂能去之。将与余沉结相终始也。余亦不敢望其全祛。而要得其差轻时节。稍治自家工夫。不至于都了放却则幸矣。闻于人则或言自己溺颇利。以此得已其沉痼之疾者有之。虽或不能快可。而少犹责其轻歇之效云。余于是乃如人言。每日自早至脯。起旋时。未尝不以一大碗满满引饮。或于出入有事之际。不无一二时虚抛。而竟日置之者。盖无几焉。自去秋至今夏。殆周一年矣。则亦不可谓都无事。向之瀜滞宛转不下者。今或消散。有时往来于中。而不至大不堪。既自觉其如此。其所以自治者。益不懈。人或谓之良苦。且少缓而亦不之顾也。仍窃自贺曰。余之半生虚了者。实由此病祟之。悔恨叹咜已不可言。自今以往。庶几复得如他人之强力无疾者。则吾事犹或有所望也。古人有谓收之桑榆。矧余年虽大。而不至桑榆者耶。
凡人之禀既高。而生仍诗礼之门。其所以目视耳听之间。起居坐立之际。率有绳墨以程之。而靡他闹热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9H 页
 心目之物。以引其所欲焉。夫如是而至乎成立。则其心地不𥷋于收拾。而自然反复入身来。其容皃不𥷋于检束。而自然俨庄而远暴慢。不知世间更有甚夺志可欲底物事。虽或遇之。而内重外轻之分。既已截然。则彼所谓夺志可欲者。自我视之。则不过乎浮云之过太空。是乌足动我一毫发哉。如此者固无大家费力。而易能向前去。其所造之浅深。则又在乎智愚明暗之如何。而终无失路伥伥之患矣。若夫自少年时出入摇荡于驳杂粗疏之境。一味度日。不知此外有何事业。忽然有窾盈之少知觉。即知吾所行者不是。颇欲图改前愆。以自修为。而亦未知所由之路。彷徨蹜踯者。又太半矣。此则与向所云。大异焉。必资师友讲劘之益。兼济以用力之百千乎人。然后庶获有所立。不若是。则其所谓有志者。不免乎苟此自欺之归。虽有一二可称之善。而此不足偿其所遗失也。此古人之学。必先致知者。以其明识此理之所在。由此便是。不由此便不是。则断然行之而不疑也。愚之病实在于鄙朴昏昧。自弱冠。粗欲勉其为己之实。而行之既不力。神识又尔茸阘。于寻常世间事。亦皆漫不知何状。则其于圣贤之言语道理。尤无一管之见也。
心目之物。以引其所欲焉。夫如是而至乎成立。则其心地不𥷋于收拾。而自然反复入身来。其容皃不𥷋于检束。而自然俨庄而远暴慢。不知世间更有甚夺志可欲底物事。虽或遇之。而内重外轻之分。既已截然。则彼所谓夺志可欲者。自我视之。则不过乎浮云之过太空。是乌足动我一毫发哉。如此者固无大家费力。而易能向前去。其所造之浅深。则又在乎智愚明暗之如何。而终无失路伥伥之患矣。若夫自少年时出入摇荡于驳杂粗疏之境。一味度日。不知此外有何事业。忽然有窾盈之少知觉。即知吾所行者不是。颇欲图改前愆。以自修为。而亦未知所由之路。彷徨蹜踯者。又太半矣。此则与向所云。大异焉。必资师友讲劘之益。兼济以用力之百千乎人。然后庶获有所立。不若是。则其所谓有志者。不免乎苟此自欺之归。虽有一二可称之善。而此不足偿其所遗失也。此古人之学。必先致知者。以其明识此理之所在。由此便是。不由此便不是。则断然行之而不疑也。愚之病实在于鄙朴昏昧。自弱冠。粗欲勉其为己之实。而行之既不力。神识又尔茸阘。于寻常世间事。亦皆漫不知何状。则其于圣贤之言语道理。尤无一管之见也。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1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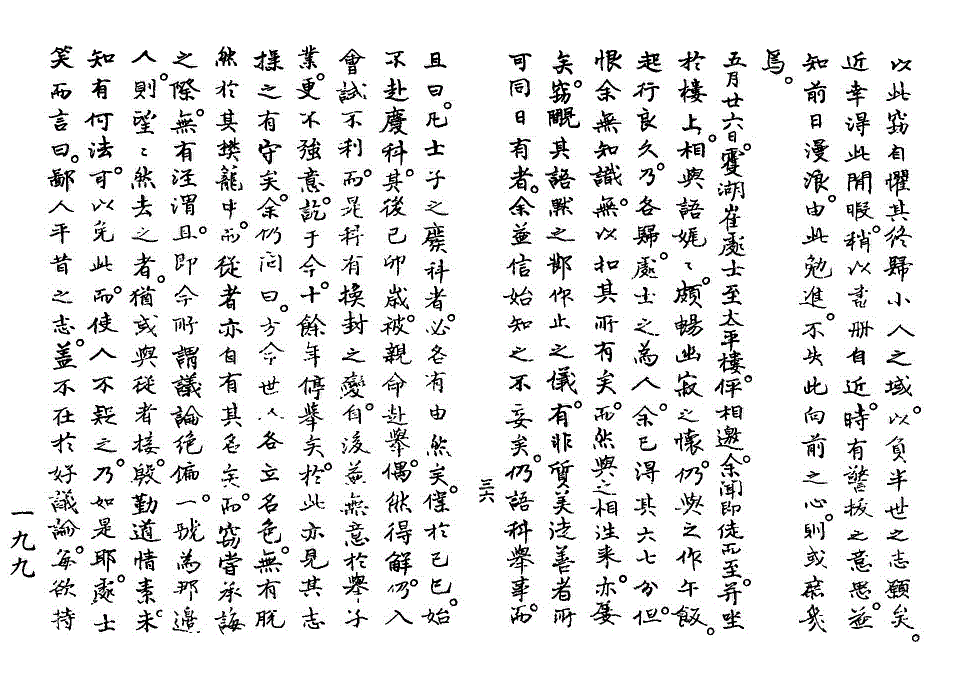 以此窃自惧其终归小人之域。以负半世之志愿矣。近幸得此閒暇。稍以书册自近。时有警拔之意思。益知前日漫浪。由此勉进。不失此向前之心。则或庶几焉。
以此窃自惧其终归小人之域。以负半世之志愿矣。近幸得此閒暇。稍以书册自近。时有警拔之意思。益知前日漫浪。由此勉进。不失此向前之心。则或庶几焉。五月廿六日。䨥湖崔处士至太平楼。伻相邀。余闻即徒而至。并坐于楼上。相与语娓娓。颇畅幽寂之怀。仍与之作午饭。起行良久。乃各归。处士之为人。余已得其六七分。但恨余无知识。无以扣其所有矣。而然与之相往来。亦屡矣。窃覸其语默之节作止之仪。有非质美徒善者所可同日有者。余益信始知之不妄矣。仍语科举事。而且曰。凡士子之废科者。必各有由然矣。仆于己巳。始不赴庆科。其后己卯岁。被亲命赴举。偶然得解。仍入会试不利。而是科有换封之变。自后益无意于举子业。更不强意。讫于今。十馀年停举矣。于此亦见其志操之有守矣。余仍问曰。方今世人各立名色。无有脱然于其樊笼中。而从者亦自有其名矣。而窃尝承诲之际。无有泾渭。且即今所谓议论绝偏。一号为那边人。则望望然去之者。犹或与从者接。殷勤道情素。未知有何法。可以免此。而使人不疑之。乃如是耶。处士笑而言曰。鄙人平昔之志。盖不在于好议论。每欲持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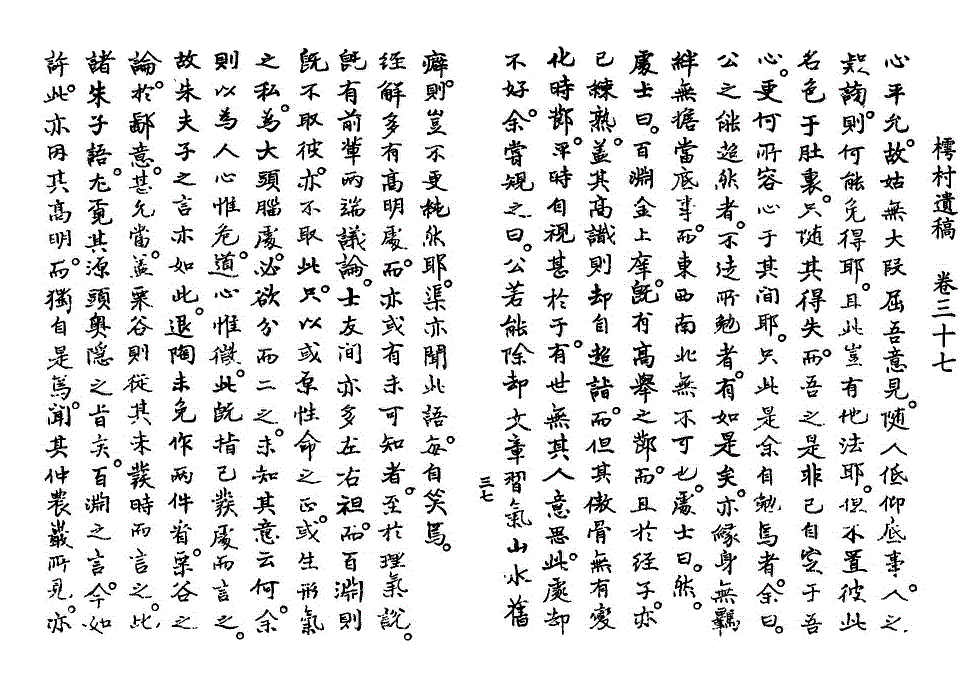 心平允。故姑无大段屈吾意见。随人低仰底事。人之疑谤。则何能免得耶。且此岂有他法耶。但不置彼此名色于肚里。只随其得失。而吾之是非已自定于吾心。更何所容心于其间耶。只此是余自勉焉者。余曰。公之能超然者。不徒所勉者。有如是矣。亦缘身无羁绊无担当底事。而东西南北无不可也。处士曰。然。
心平允。故姑无大段屈吾意见。随人低仰底事。人之疑谤。则何能免得耶。且此岂有他法耶。但不置彼此名色于肚里。只随其得失。而吾之是非已自定于吾心。更何所容心于其间耶。只此是余自勉焉者。余曰。公之能超然者。不徒所勉者。有如是矣。亦缘身无羁绊无担当底事。而东西南北无不可也。处士曰。然。处士曰。百渊金上庠。既有高举之节。而且于经子。亦已练熟。盖其高识则却自超诣。而但其傲骨无有变化时节。平时自视甚于于。有世无其人意思。此处却不好。余尝规之曰。公若能除却文章习气山水旧癖。则岂不更纯然耶。渠亦闻此语。每自笑焉。
经解多有高明处。而亦或有未可知者。至于理气说。既有前辈两端议论。士友间亦多左右袒。而百渊则既不取彼。亦不取此。只以或原性命之正。或生形气之私。为大头脑处。必欲分而二之。未知其意云何。余则以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既指已发处而言之。故朱夫子之言亦如此。退陶未免作两件看。栗谷之论。于鄙意。甚允当。盖栗谷则从其未发时而言之。比诸朱子语。尤觅其源头奥隐之旨矣。百渊之言。今如许。此亦因其高明。而独自是焉。闻其仲农岩所见。亦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0L 页
 与百渊同云矣。
与百渊同云矣。余问曰。公之平昔所与还往。而以文学道义。相推让者。未知有几许人耶。答曰。愚自少时。无他师友间往来者。而安君重谦有所见。且笃实。是余所尝友善。而丁进善时翰甫。虽无师受之分。而平日好其为人。心尝推服焉。丁公亦曾至余家。留一两日。余亦至其家。信宿而还矣。公未尝自处以儒者。而多自韬晦。虽从其外面观之。亦是长者人矣。晚年尤留意于此事。所见亦或明快。且其持敬工夫。则虽古人有难能者。竟日危坐。少无惰容。起兴坐立之际。未或放过。至于手容。亦必有常。既措于一处。更无动转。是亦心定之所致然也。余曰。此尹和靖能之。盖独得程门一敬字。从事久而得如此。则丁公之持敬工夫。可谓无让于古人矣。
六月。余性懒。虽在洛社。亦罕与游从。今自岭东而还。间阔朋旧亦数月矣。而余既不告其去来。人亦不屑而肯来也。尹仲和适一过余。且要一夜之款。余肯之。期以他夜。至十五日。余至伯父所住寓礼曹直房。抵暮徒而归。力且稀。仍入少陵。仲和独在。无他人焉。是夜月明。轩户岑寂。又得良朋。与之叙话。于鄙分。尤忻幸也。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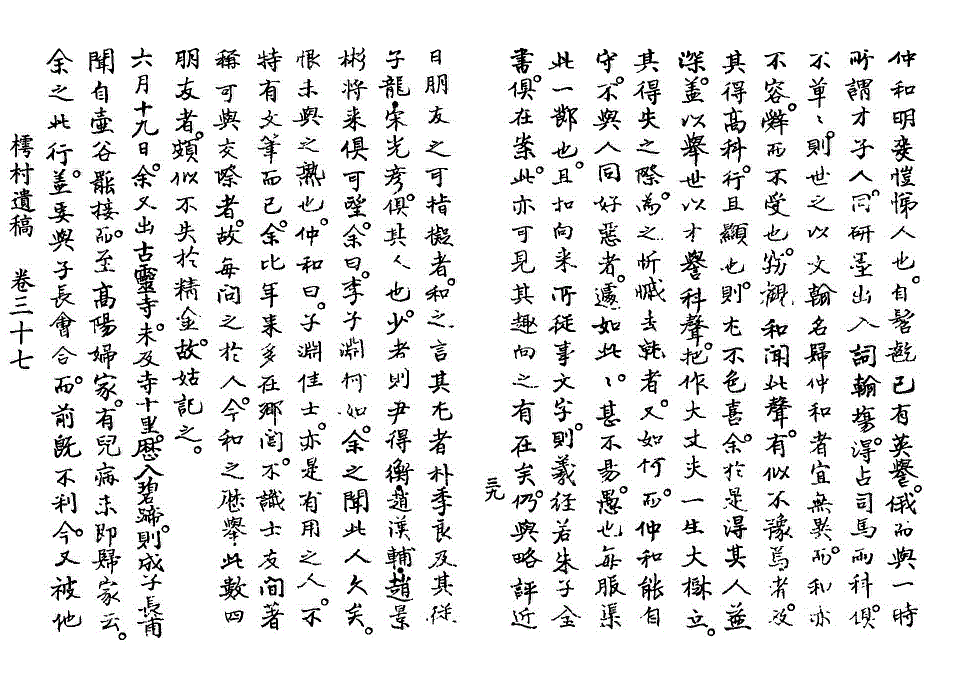 仲和明爽恺悌人也。自髫龁(一作龀)已有英誉。俄而与一时所谓才子人。同研墨出入词翰场。得占司马两科。俱不草草。则世之以文翰名归仲和者宜无异。而和亦不容。辞而不受也。窃观和闻此声。有似不豫焉者。及其得高科。行且显也。则尤不色喜。余于是得其人益深。盖以举世以才誉科声。把作大丈夫一生大树立。其得失之际。为之忻戚去就者。又如何。而仲和能自守。不与人同好恶者。遽如此。此甚不易。愚也每服渠此一节也。且扣向来所从事文字。则羲经若朱子全书。俱在案。此亦可见其趣向之有在矣。仍与略评近日朋友之可指拟者。和之言其尤者朴季良及其从子龙,宋光彦。俱其人也。少者则尹得衡,赵汉辅,赵景彬将来俱可望。余曰。李子渊何如。余之闻此人久矣。恨未与之熟也。仲和曰。子渊佳士。亦是有用之人。不特有文笔而已。余比年来多在乡闾。不识士友间著称可与交际者。故每问之于人。今和之历举此数四朋友者。颇似不失于精金。故姑记之。
仲和明爽恺悌人也。自髫龁(一作龀)已有英誉。俄而与一时所谓才子人。同研墨出入词翰场。得占司马两科。俱不草草。则世之以文翰名归仲和者宜无异。而和亦不容。辞而不受也。窃观和闻此声。有似不豫焉者。及其得高科。行且显也。则尤不色喜。余于是得其人益深。盖以举世以才誉科声。把作大丈夫一生大树立。其得失之际。为之忻戚去就者。又如何。而仲和能自守。不与人同好恶者。遽如此。此甚不易。愚也每服渠此一节也。且扣向来所从事文字。则羲经若朱子全书。俱在案。此亦可见其趣向之有在矣。仍与略评近日朋友之可指拟者。和之言其尤者朴季良及其从子龙,宋光彦。俱其人也。少者则尹得衡,赵汉辅,赵景彬将来俱可望。余曰。李子渊何如。余之闻此人久矣。恨未与之熟也。仲和曰。子渊佳士。亦是有用之人。不特有文笔而已。余比年来多在乡闾。不识士友间著称可与交际者。故每问之于人。今和之历举此数四朋友者。颇似不失于精金。故姑记之。六月十九日。余又出古灵寺。未及寺十里。历入碧蹄。则成子长甫闻自壶谷罢接。而至高阳妇家。有儿病未即归家云。余之此行。盖要与子长会合。而前既不利。今又被他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1L 页
 有冗。不即盍簪。殊可怅然。然余在桃第。凡百滚冗。日来侵人。不但文字之废置。酬接之馀。自家一个身心。亦不能顿着得下。常如风纛摇荡中灭没过去。如是。宁复有好意思。自能操存不放底时节耶。故屡欲抽身适他。做得旬月工夫。不只为此举子业而已也。于其静暇之时。必欲以古人文字之实切者。以自近而性。又于朱子节要书。常尊信焉。乃要少主人辈倩此书。则辞以李斯文道载已持去。而叙九册袱在此。其中盖有节要一秩云。余曰。叙九物亦余有也。仍取其十册。纳衾中而来。成君且笑曰。顷者家叔与叙九同会时。李君去高阳。伻要此书。则叙九语家叔曰。吾辈方此汨头于科臼中。意不能在他。而此公乃能取此不急时之书册。如吾辈在纷汨中者。宁不汗颜。仍又自笑云云。余闻李公之为也。心颇向仰。而且曰。李之当此科儒奔忙时。取如许文字自看。殊甚不易。可想其閒静有馀也。若余者。安有李公意思。而亦取此书耶。只欲于此不及做业时。早晚遮眼。则犹胜于观他浮薄世俗文章耳。吾与李君取此书。事则同而意不相似。成生之欲比而同之。盖犹不谅余若是低下也。古人谓科举之害曰。不患妨工。惟患夺志。余尝言科
有冗。不即盍簪。殊可怅然。然余在桃第。凡百滚冗。日来侵人。不但文字之废置。酬接之馀。自家一个身心。亦不能顿着得下。常如风纛摇荡中灭没过去。如是。宁复有好意思。自能操存不放底时节耶。故屡欲抽身适他。做得旬月工夫。不只为此举子业而已也。于其静暇之时。必欲以古人文字之实切者。以自近而性。又于朱子节要书。常尊信焉。乃要少主人辈倩此书。则辞以李斯文道载已持去。而叙九册袱在此。其中盖有节要一秩云。余曰。叙九物亦余有也。仍取其十册。纳衾中而来。成君且笑曰。顷者家叔与叙九同会时。李君去高阳。伻要此书。则叙九语家叔曰。吾辈方此汨头于科臼中。意不能在他。而此公乃能取此不急时之书册。如吾辈在纷汨中者。宁不汗颜。仍又自笑云云。余闻李公之为也。心颇向仰。而且曰。李之当此科儒奔忙时。取如许文字自看。殊甚不易。可想其閒静有馀也。若余者。安有李公意思。而亦取此书耶。只欲于此不及做业时。早晚遮眼。则犹胜于观他浮薄世俗文章耳。吾与李君取此书。事则同而意不相似。成生之欲比而同之。盖犹不谅余若是低下也。古人谓科举之害曰。不患妨工。惟患夺志。余尝言科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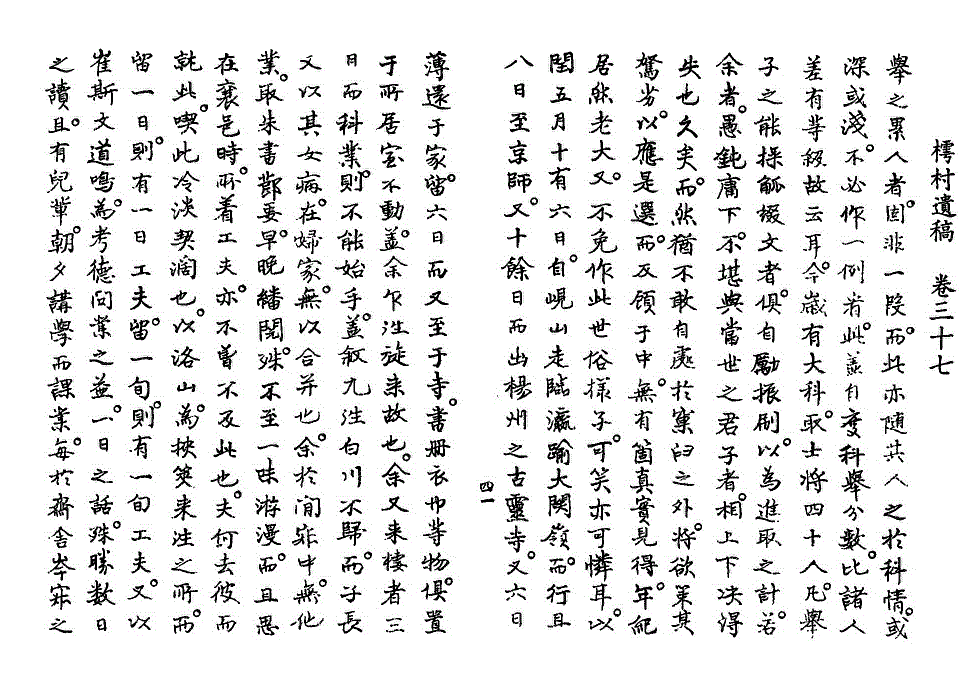 举之累人者。固非一段。而此亦随其人之于科情。或深或浅。不必作一例看。此盖自度科举分数。比诸人差有等级故云耳。今岁有大科。取士将四十人。凡举子之能操觚缀文者。俱自励振刷。以为进取之计。若余者。愚钝庸下。不堪与当世之君子者。相上下决得失也久矣。而然犹不敢自处于窠臼之外。将欲策其驽劣。以应是选。而反顾于中。无有个真实见得。年纪居然老大。又不免作此世俗㨾子。可笑亦可怜耳。以闰五月十有六日。自岘山走临瀛踰大关岭。而行且八日至京师。又十馀日而出杨州之古灵寺。又六日薄还于家。留六日而又至于寺。书册衣巾等物。俱置于所居室不动。盖余乍往旋来故也。余又来栖者三日而科业。则不能始手。盖叙九往白川不归。而子长又以其女病。在妇家。无以合并也。余于閒寂中。无他业。取朱书节要。早晚翻阅。殊不至一味游漫。而且思在襄邑时。所着工夫。亦不曾不及此也。夫何去彼而就此。吃此冷淡契阔也。以洛山。为挟筴来往之所。而留一日。则有一日工夫。留一旬。则有一旬工夫。又以崔斯文道鸣。为考德问业之益。一日之话。殊胜数日之读。且有儿辈。朝夕讲学而课业。每于斋舍岑寂之
举之累人者。固非一段。而此亦随其人之于科情。或深或浅。不必作一例看。此盖自度科举分数。比诸人差有等级故云耳。今岁有大科。取士将四十人。凡举子之能操觚缀文者。俱自励振刷。以为进取之计。若余者。愚钝庸下。不堪与当世之君子者。相上下决得失也久矣。而然犹不敢自处于窠臼之外。将欲策其驽劣。以应是选。而反顾于中。无有个真实见得。年纪居然老大。又不免作此世俗㨾子。可笑亦可怜耳。以闰五月十有六日。自岘山走临瀛踰大关岭。而行且八日至京师。又十馀日而出杨州之古灵寺。又六日薄还于家。留六日而又至于寺。书册衣巾等物。俱置于所居室不动。盖余乍往旋来故也。余又来栖者三日而科业。则不能始手。盖叙九往白川不归。而子长又以其女病。在妇家。无以合并也。余于閒寂中。无他业。取朱书节要。早晚翻阅。殊不至一味游漫。而且思在襄邑时。所着工夫。亦不曾不及此也。夫何去彼而就此。吃此冷淡契阔也。以洛山。为挟筴来往之所。而留一日。则有一日工夫。留一旬。则有一旬工夫。又以崔斯文道鸣。为考德问业之益。一日之话。殊胜数日之读。且有儿辈。朝夕讲学而课业。每于斋舍岑寂之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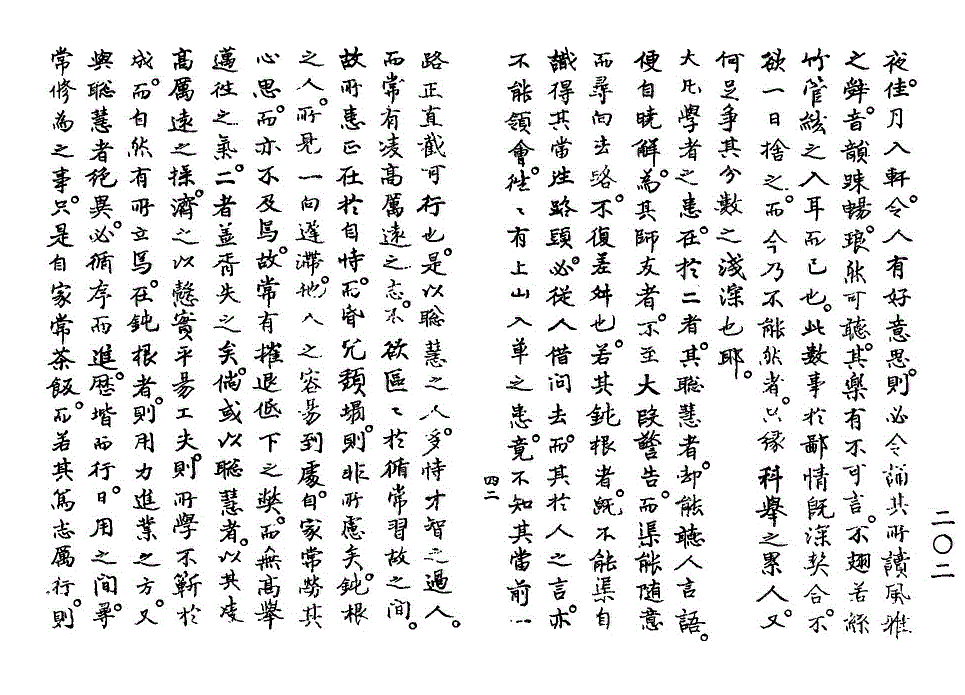 夜。佳月入轩。令人有好意思。则必令诵其所读风雅之辞。音韵疏畅。琅然可听。其乐有不可言。不翅若丝竹管弦之入耳而已也。此数事于鄙情既深契合。不欲一日舍之。而今乃不能然者。只缘科举之累人。又何足争其分数之浅深也耶。
夜。佳月入轩。令人有好意思。则必令诵其所读风雅之辞。音韵疏畅。琅然可听。其乐有不可言。不翅若丝竹管弦之入耳而已也。此数事于鄙情既深契合。不欲一日舍之。而今乃不能然者。只缘科举之累人。又何足争其分数之浅深也耶。大凡学者之患。在于二者。其聪慧者。却能听人言语。便自晓解。为其师友者。不至大段警告。而渠能随意而寻向去路。不复差舛也。若其钝根者。既不能渠自识得其当往路头。必从人借问去。而其于人之言。亦不能领会。往往有上山入草之患。竟不知其当前一路正直截可行也。是以聪慧之人。多恃才智之过人。而常有凌高厉远之志。不欲区区于循常习故之间。故所患正在于自恃。而昏冗颓塌。则非所虑矣。钝根之人。所见一向迟滞。他人之容易到处。自家常劳其心思。而亦不及焉。故常有摧退低下之弊。而无高举迈往之气。二者盖胥失之矣。倘或以聪慧者。以其凌高厉远之操。济之以悫实平易工夫。则所学不𥷋于成。而自然有所立焉。在钝根者。则用力进业之方。又与聪慧者绝异。必循序而进。历阶而行。日用之间。寻常修为之事。只是自家常茶饭。而若其笃志厉行。则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3H 页
 又必勇往直前。血战相似。方可有可观处。不然。祗是颓堕而止已。苟且而止已。
又必勇往直前。血战相似。方可有可观处。不然。祗是颓堕而止已。苟且而止已。余之出古灵寺也。既告家人以做科业。而及至则子长不至。余又无他朋友可与同事者也。始来之计。虽颇爽误。而窃幸于此暇时。犹可收拾精神。看得古人文字。乃抽朱子节要。一例看过。而于其寻常与人酬酢处。不过一二遍。至于讲说义理指切工夫有可以玩味而体验者。则亦或更看一二遍。余性既钝根。且苦无记性。凡诸文字。虽读至百遍。而犹不能领会。则于此草草过眼者。又可𥷋其记得耶。然而看此等文字事体。与他册有异。不敢以怠慢不敬之心。肆然披阅。故翻览之际。既自稍好戒敕底意思。而且遇其言语之切近。论人病败与其学问趍舍之得失。心地邪正之去就。说得他人所不能形容者。既斥其病根之所在。而仍又为之针焫。而下其所当施之药。虽使其方病者见之。亦可晓然。渠之寻常痛楚。不堪叫苦。而犹不能知其病在于体骸脏腑间某处。只自呼人乞瘳而已。于是焉一见之而得其受病处。从其浅深缓急而治之。或灸或药。无一失其当焉。此非理明心定施措如宜者。讵能若是哉。且其往复论说。只在于人伦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3L 页
 日用当行之事。不复引其别件难理会。令学者究索也。故吟诵之间。自见意味无穷。如欲将取作自家己物。亦易为力矣。余曾亦见此书。当其见时。不无一二所见。且于躬行上。有些体行者。而持志不专。旋又失却。则复如曩时伎俩矣。日来看得。颇觉于身心有警省振厉处。默思向来多少走作。不知有汗浃背也。自此能寻向上去。不迷路脉。则或能免小人之归欤。
日用当行之事。不复引其别件难理会。令学者究索也。故吟诵之间。自见意味无穷。如欲将取作自家己物。亦易为力矣。余曾亦见此书。当其见时。不无一二所见。且于躬行上。有些体行者。而持志不专。旋又失却。则复如曩时伎俩矣。日来看得。颇觉于身心有警省振厉处。默思向来多少走作。不知有汗浃背也。自此能寻向上去。不迷路脉。则或能免小人之归欤。余性既弛缓。且于一切世味。未甚浸淫。自童子时。人或谓之沉着可以有为。余亦不自知。而窃自以为人言之或彷佛也。遽因其弛缓而以𥷋进步。如是且十许年。卒未有得。只是旧来面目。而若其向进不已之意。则却颇消歇。又不如往时矣。或于中夜寐觉之时。觉得如此。怛然惊惧。不知所以为计。且念自己性偏处。欲克将去。则盖在和缓上错了路头也。人之迟延歇后者。自他人视之。则颇似宽平无轻薄浮侠之气。固足以称之。而在己则却不然。其所以进取之者。惟当矫其所偏。必如弦韦之佩。然后乃可有立耳。如仆者。亦于其有意之初。直将以刚毅果敢明白直截底一件道理。既令振刷而奋跃之。又从以持养不懈。一味寻向上去。到得十数年久之。无前却之态。则似不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4H 页
 至作此今日㨾子矣。愧惕闷惧。无地自容。然此一段慨惋意思。亦于静里。收拾身心。因其羞恶中来。而只如泉之始达而已。若复出入纷汨场中。日用事物。交至而沓攻。自家一个身心。不知顿放得底处。则只此一时未泯之好意思。亦将漂散。又入荡荡地去矣。苟非因而长之。培而养之。一日十二辰中。常自照管。不令些儿放失。而浸沉悠久。提掇安顿。则其存者几时。而不存者无几时矣。噫。人常以死生为一大事。然而凡天下不知几何人。只自蚩蚩泯泯。则又不可以其生为可贵。而于其中。有可以自好无愧者。则是诚不负造化者。所以赋余者已不然。则吾不欲有腼面目于天地中。作一蠹以害人也。
至作此今日㨾子矣。愧惕闷惧。无地自容。然此一段慨惋意思。亦于静里。收拾身心。因其羞恶中来。而只如泉之始达而已。若复出入纷汨场中。日用事物。交至而沓攻。自家一个身心。不知顿放得底处。则只此一时未泯之好意思。亦将漂散。又入荡荡地去矣。苟非因而长之。培而养之。一日十二辰中。常自照管。不令些儿放失。而浸沉悠久。提掇安顿。则其存者几时。而不存者无几时矣。噫。人常以死生为一大事。然而凡天下不知几何人。只自蚩蚩泯泯。则又不可以其生为可贵。而于其中。有可以自好无愧者。则是诚不负造化者。所以赋余者已不然。则吾不欲有腼面目于天地中。作一蠹以害人也。凡学者。不曾向里做工夫。而只于其外面修饰边幅。以侈人目者。固有内外不相副之病。毕竟亦不自进。而但自欺欺人。无有是处耳。此一种人既不足言。而又有与此不相似者。而自谓夷旷平易。不区区于绳约彀律之间。而其所以操守于里面云者。自如也。其言固如此。从而审其辞气动止之际。果尔坦朴率易。全无拘检底气习。若此者。其真可谓得平常道理。而循循可与入于向上事耶。曰。是乌足言。是不过将来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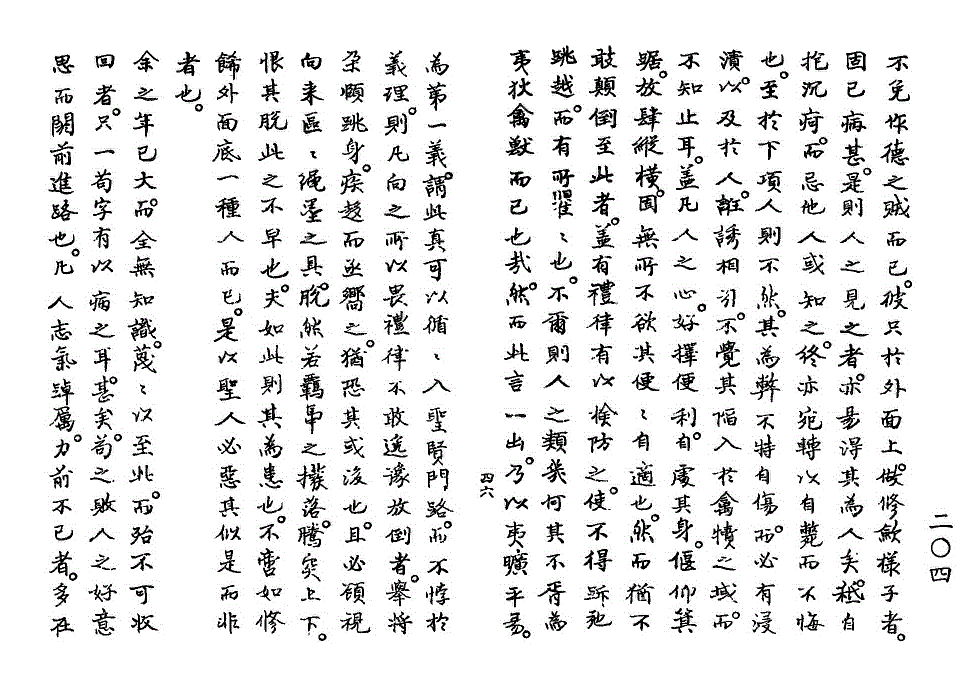 不免作德之贼而已。彼只于外面上。做修敛样子者。固已病甚。是则人之见之者。亦易得其为人矣。秪自抱沉疴。而忌他人或知之。终亦宛转以自毙而不悔也。至于下项人则不然。其为弊不特自伤。而必有浸渍。以及于人。诳诱相引。不觉其陷入于禽犊之域。而不知止耳。盖凡人之心。好择便利。自处其身。偃仰箕踞。放肆纵横。固无所不欲其便便自适也。然而犹不敢颠倒至此者。盖有礼律有以捡防之。使不得跅弛跳越。而有所瞿瞿也。不尔则人之类几何其不胥为夷狄禽兽而已也哉。然而此言一出。乃以夷旷平易。为第一义。谓此真可以循循入圣贤门路。而不悖于义理。则凡向之所以畏礼律不敢逸豫放倒者。举将朵颐跳身。疾趍而亟向之。犹恐其或后也。且必顾视向来区区绳墨之具。脱然若羁絷之拨落。腾突上下。恨其脱此之不早也。夫如此则其为患也。不啻如修饰外面底一种人而已。是以圣人必恶其似是而非者也。
不免作德之贼而已。彼只于外面上。做修敛样子者。固已病甚。是则人之见之者。亦易得其为人矣。秪自抱沉疴。而忌他人或知之。终亦宛转以自毙而不悔也。至于下项人则不然。其为弊不特自伤。而必有浸渍。以及于人。诳诱相引。不觉其陷入于禽犊之域。而不知止耳。盖凡人之心。好择便利。自处其身。偃仰箕踞。放肆纵横。固无所不欲其便便自适也。然而犹不敢颠倒至此者。盖有礼律有以捡防之。使不得跅弛跳越。而有所瞿瞿也。不尔则人之类几何其不胥为夷狄禽兽而已也哉。然而此言一出。乃以夷旷平易。为第一义。谓此真可以循循入圣贤门路。而不悖于义理。则凡向之所以畏礼律不敢逸豫放倒者。举将朵颐跳身。疾趍而亟向之。犹恐其或后也。且必顾视向来区区绳墨之具。脱然若羁絷之拨落。腾突上下。恨其脱此之不早也。夫如此则其为患也。不啻如修饰外面底一种人而已。是以圣人必恶其似是而非者也。余之年已大。而全无知识。蔑蔑以至此。而殆不可收回者。只一苟字有以病之耳。甚矣。苟之败人之好意思而阏前进路也。凡人志气踔厉。力前不已者。多在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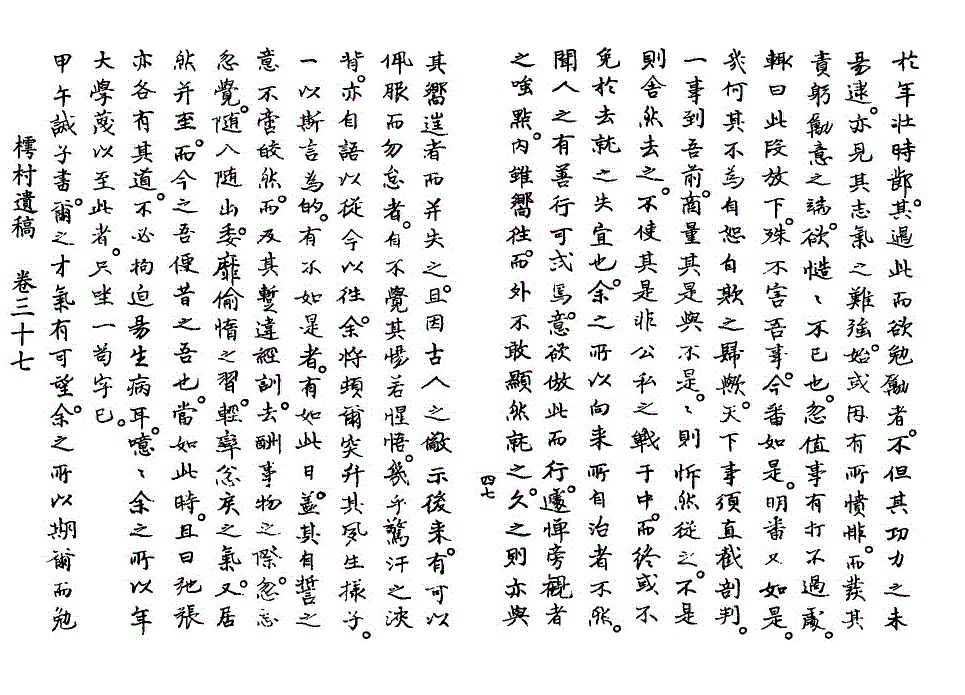 于年壮时节。其过此而欲勉励者。不但其功力之未易逮。亦见其志气之难强。始或因有所愤悱。而发其责躬励意之端。欲慥慥不已也。忽值事有打不过处。辄曰此段放下。殊不害吾事。今番如是。明番又如是。几何其不为自恕自欺之归欤。天下事须直截剖判。一事到吾前。商量其是与不是。是则忻然从之。不是则舍然去之。不使其是非公私之战于中。而终或不免于去就之失宜也。余之所以向来所自治者不然。闻人之有善行可式焉。意欲仿此而行。遽惮旁观者之嗤点。内虽向往。而外不敢显然就之。久之则亦与其向𨓏者而并失之。且因古人之儆示后来。有可以佩服而勿怠者。自不觉其惕若惺悟。几乎惊汗之浃背。亦自语以从今以往。余将顿尔突弁其夙生㨾子。一以斯言为的。有不如是者。有如此日。盖其自誓之意不啻皎然。而及其暂违经训。去酬事物之际。忽忘忽觉。随入随出。委靡偷惰之习。轻率忿戾之气。又居然并至。而今之吾便昔之吾也。当如此时。且曰弛张亦各有其道。不必拘迫易生病耳。噫噫余之所以年大学蔑以至此者。只坐一苟字已。
于年壮时节。其过此而欲勉励者。不但其功力之未易逮。亦见其志气之难强。始或因有所愤悱。而发其责躬励意之端。欲慥慥不已也。忽值事有打不过处。辄曰此段放下。殊不害吾事。今番如是。明番又如是。几何其不为自恕自欺之归欤。天下事须直截剖判。一事到吾前。商量其是与不是。是则忻然从之。不是则舍然去之。不使其是非公私之战于中。而终或不免于去就之失宜也。余之所以向来所自治者不然。闻人之有善行可式焉。意欲仿此而行。遽惮旁观者之嗤点。内虽向往。而外不敢显然就之。久之则亦与其向𨓏者而并失之。且因古人之儆示后来。有可以佩服而勿怠者。自不觉其惕若惺悟。几乎惊汗之浃背。亦自语以从今以往。余将顿尔突弁其夙生㨾子。一以斯言为的。有不如是者。有如此日。盖其自誓之意不啻皎然。而及其暂违经训。去酬事物之际。忽忘忽觉。随入随出。委靡偷惰之习。轻率忿戾之气。又居然并至。而今之吾便昔之吾也。当如此时。且曰弛张亦各有其道。不必拘迫易生病耳。噫噫余之所以年大学蔑以至此者。只坐一苟字已。甲午诫子书。尔之才气有可望。余之所以期尔而勉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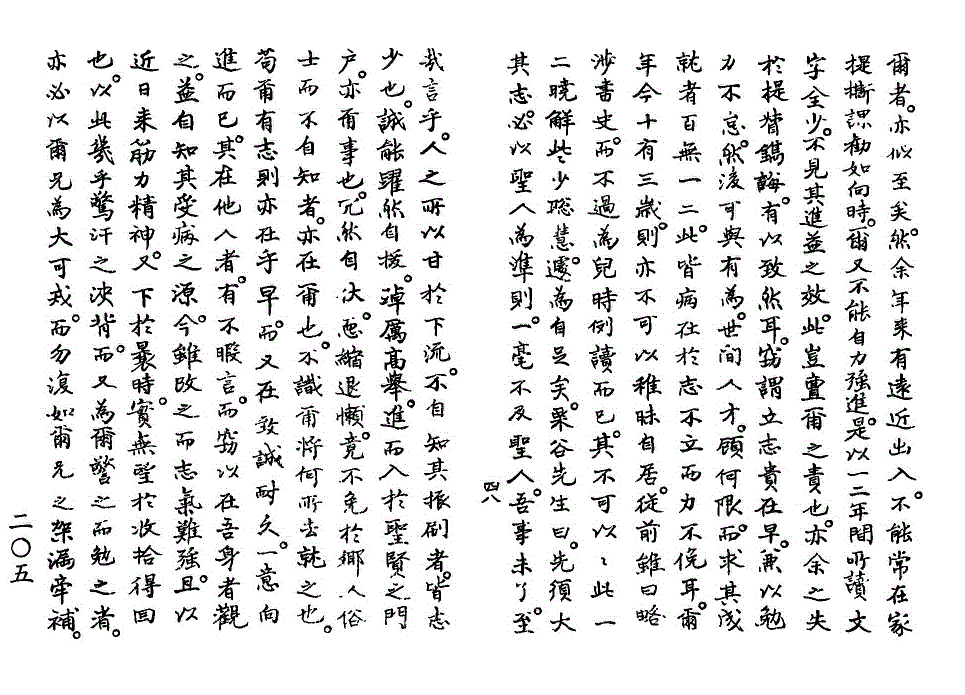 尔者。亦似至矣。然余年来有远近出入。不能常在家提撕课劝如向时。尔又不能自力强进。是以一二年间所读文字全少。不见其进益之效。此岂亶尔之责也。亦余之失于提督镌诲。有以致然耳。窃谓立志贵在早。兼以勉力不怠。然后可与有为。世间人才。顾何限。而求其成就者百无一二。此皆病在于志不立而力不俛耳。尔年今十有三岁。则亦不可以稚昧自居。从前虽曰略涉书史。而不过为儿时例读而已。其不可以以此一二晓解些少聪慧。遽为自足矣。栗谷先生曰。先须大其志。必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吾事未了。至哉言乎。人之所以甘于下流。不自知其振刷者。皆志少也。诚能跃然自拔。踔厉高举。进而入于圣贤之门户。亦尔事也。冗然自伏。恧缩退懒。竟不免于乡人俗士而不自知者。亦在尔也。不识尔将何所去就之也。苟尔有志则亦在乎早。而又在致诚耐久。一意向进而已。其在他人者。有不暇言。而窃以在吾身者观之。益自知其受病之源。今虽改之而志气难强。且以近日来筋力精神。又下于曩时。实无望于收拾得回也。以此几乎惊汗之浃背。而又为尔警之而勉之者。亦必以尔兄为大可戒。而勿复如尔兄之架漏牵补。
尔者。亦似至矣。然余年来有远近出入。不能常在家提撕课劝如向时。尔又不能自力强进。是以一二年间所读文字全少。不见其进益之效。此岂亶尔之责也。亦余之失于提督镌诲。有以致然耳。窃谓立志贵在早。兼以勉力不怠。然后可与有为。世间人才。顾何限。而求其成就者百无一二。此皆病在于志不立而力不俛耳。尔年今十有三岁。则亦不可以稚昧自居。从前虽曰略涉书史。而不过为儿时例读而已。其不可以以此一二晓解些少聪慧。遽为自足矣。栗谷先生曰。先须大其志。必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吾事未了。至哉言乎。人之所以甘于下流。不自知其振刷者。皆志少也。诚能跃然自拔。踔厉高举。进而入于圣贤之门户。亦尔事也。冗然自伏。恧缩退懒。竟不免于乡人俗士而不自知者。亦在尔也。不识尔将何所去就之也。苟尔有志则亦在乎早。而又在致诚耐久。一意向进而已。其在他人者。有不暇言。而窃以在吾身者观之。益自知其受病之源。今虽改之而志气难强。且以近日来筋力精神。又下于曩时。实无望于收拾得回也。以此几乎惊汗之浃背。而又为尔警之而勉之者。亦必以尔兄为大可戒。而勿复如尔兄之架漏牵补。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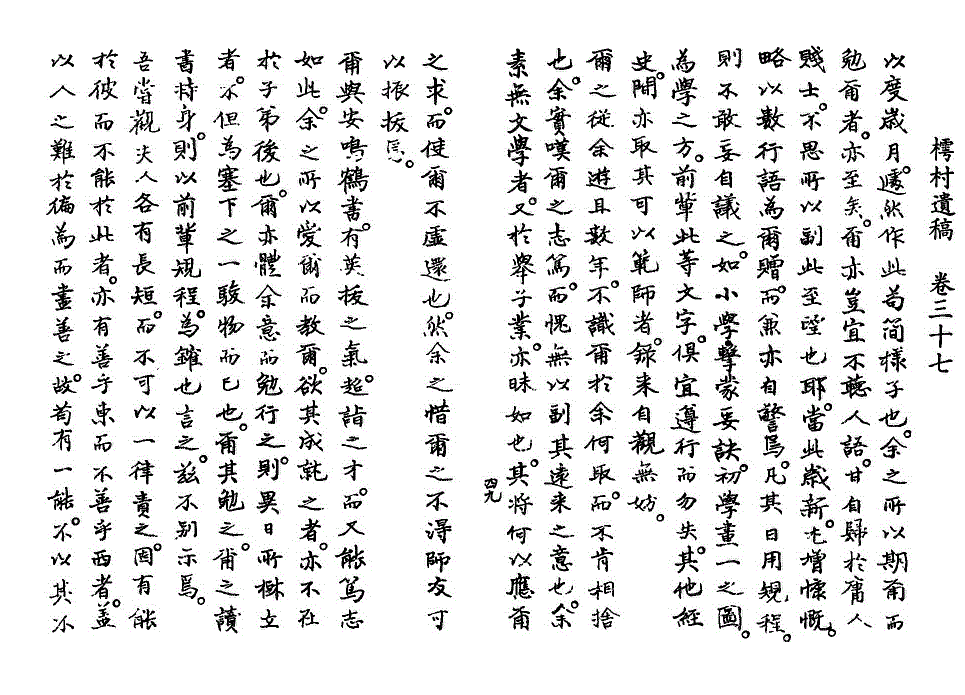 以度岁月。遽然作此苟简样子也。余之所以期尔而勉尔者。亦至矣。尔亦岂宜不听人语。甘自归于庸人贱士。不思所以副此至望也耶。当此岁新。尤增慷慨。略以数行语为尔赠。而兼亦自警焉。凡其日用规程。则不敢妄自议之。如小学,击蒙要诀。初学画一之图。为学之方。前辈此等文字。俱宜遵行而勿失。其他经史。间亦取其可以范师者。录来自观无妨。
以度岁月。遽然作此苟简样子也。余之所以期尔而勉尔者。亦至矣。尔亦岂宜不听人语。甘自归于庸人贱士。不思所以副此至望也耶。当此岁新。尤增慷慨。略以数行语为尔赠。而兼亦自警焉。凡其日用规程。则不敢妄自议之。如小学,击蒙要诀。初学画一之图。为学之方。前辈此等文字。俱宜遵行而勿失。其他经史。间亦取其可以范师者。录来自观无妨。尔之从余游且数年。不识尔于余何取。而不肯相舍也。余实叹尔之志笃。而愧无以副其远来之意也。余素无文学者。又于举子业。亦昧如也。其将何以应尔之求。而使尔不虚还也。然余之惜尔之不得师友可以振拔焉。
尔与安鸣鹤书。有英拔之气。超诣之才。而又能笃志如此。余之所以爱尔而教尔。欲其成就之者。亦不在于子弟后也。尔亦体余意而勉行之。则异日所树立者。不但为塞下之一骏物而已也。尔其勉之。尔之读书持身。则以前辈规程。为䥃也言之。玆不别示焉。
吾尝观夫人各有长短。而不可以一律责之。固有能于彼而不能于此者。亦有善乎东而不善乎西者。盖以人之难于遍为而尽善之。故苟有一能。不以其不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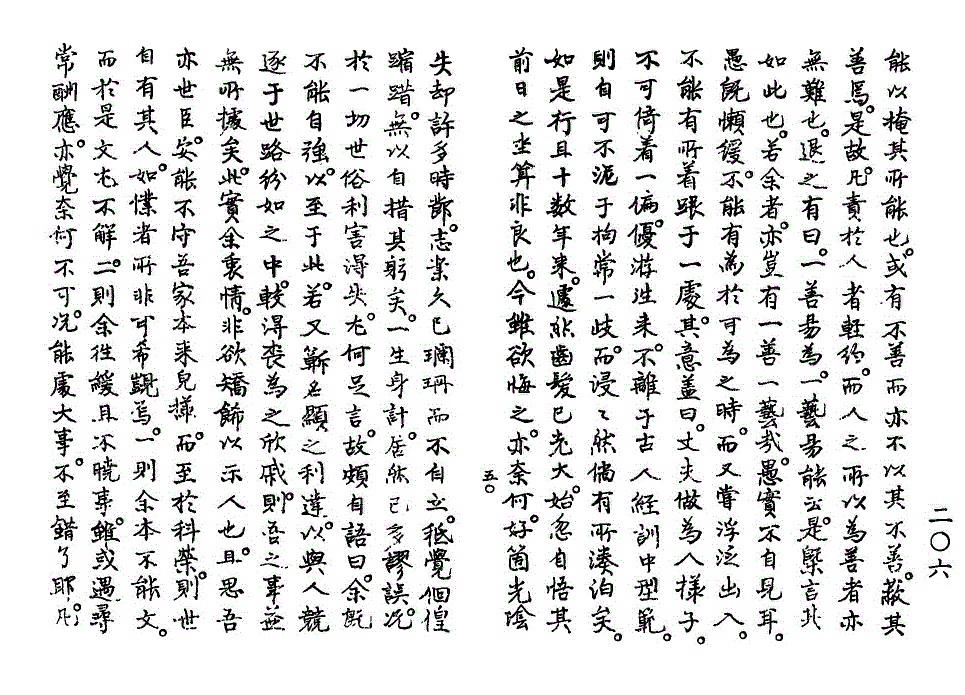 能以掩其所能也。或有不善而亦不以其不善。蔽其善焉。是故。凡责于人者轻约。而人之所以为善者亦无难也。退之有曰。一善易为。一艺易能云。是槩言其如此也。若余者。亦岂有一善一艺哉。愚实不自见耳。愚既懒缓。不能有为于可为之时。而又尝浮泛出入。不能有所着跟于一处。其意盖曰。丈夫做为人㨾子。不可倚着一偏。优游往来。不离于古人经训中型范。则自可不泥于拘常一歧。而浸浸然倘有所凑泊矣。如是行且十数年来。遽然齿发已老大。始忽自悟其前日之坐算非良也。今虽欲悔之。亦奈何。好个光阴失却许多时节。志业久已瓓珊而不自立。秪觉佪偟蹜踖。无以自措其躬矣。一生身计。居然已多谬误。况于一切世俗利害得失。尤何足言。故颇自语曰。余既不能自强。以至于此。若又𥷋名显之利达。以与人竞逐于世路纷如之中。较得丧为之欣戚。则吾之事益无所据矣。此实余衷情。非欲矫饰以示人也。且思吾亦世臣。安能不守吾家本来皃㨾。而至于科荣。则世自有其人。如仆者所非可希觊焉。一则余本不能文。而于是文尤不解。二则余往缓且不晓事。虽或遇寻常酬应。亦觉奈何不可。况能处大事。不至错了耶。凡
能以掩其所能也。或有不善而亦不以其不善。蔽其善焉。是故。凡责于人者轻约。而人之所以为善者亦无难也。退之有曰。一善易为。一艺易能云。是槩言其如此也。若余者。亦岂有一善一艺哉。愚实不自见耳。愚既懒缓。不能有为于可为之时。而又尝浮泛出入。不能有所着跟于一处。其意盖曰。丈夫做为人㨾子。不可倚着一偏。优游往来。不离于古人经训中型范。则自可不泥于拘常一歧。而浸浸然倘有所凑泊矣。如是行且十数年来。遽然齿发已老大。始忽自悟其前日之坐算非良也。今虽欲悔之。亦奈何。好个光阴失却许多时节。志业久已瓓珊而不自立。秪觉佪偟蹜踖。无以自措其躬矣。一生身计。居然已多谬误。况于一切世俗利害得失。尤何足言。故颇自语曰。余既不能自强。以至于此。若又𥷋名显之利达。以与人竞逐于世路纷如之中。较得丧为之欣戚。则吾之事益无所据矣。此实余衷情。非欲矫饰以示人也。且思吾亦世臣。安能不守吾家本来皃㨾。而至于科荣。则世自有其人。如仆者所非可希觊焉。一则余本不能文。而于是文尤不解。二则余往缓且不晓事。虽或遇寻常酬应。亦觉奈何不可。况能处大事。不至错了耶。凡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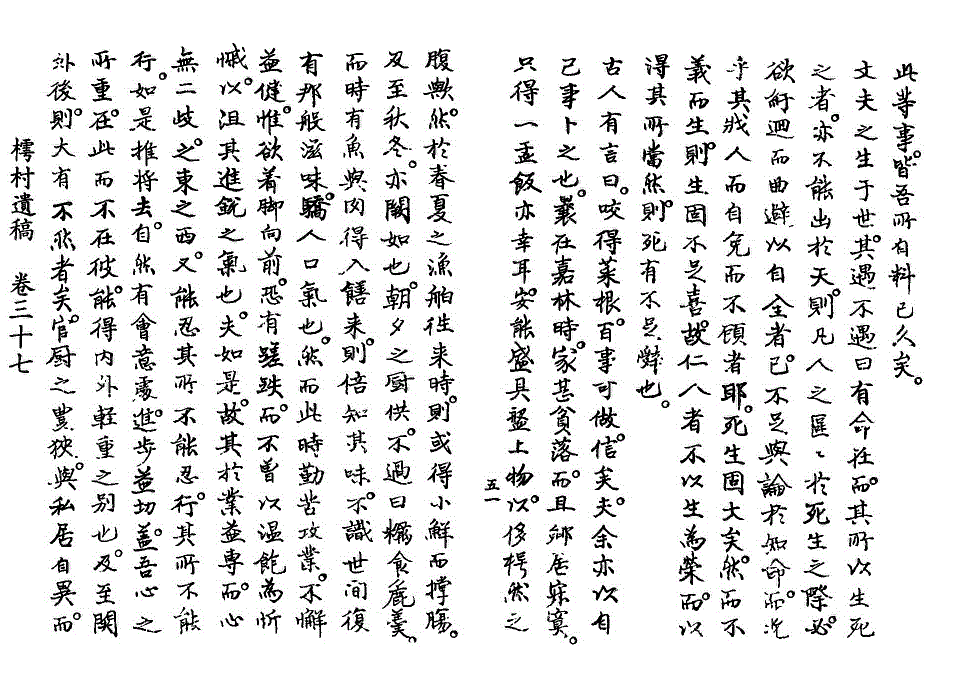 此等事。皆吾所自料已久矣。
此等事。皆吾所自料已久矣。丈夫之生于世。其遇不遇曰有命在。而其所以生死之者。亦不能出于天。则凡人之区区于死生之际。必欲纡回而曲避以自全者。已不足与论于知命。而况乎其戕人而自免而不顾者耶。死生固大矣。然而不义而生。则生固不足喜。故仁人者不以生为荣。而以得其所当然。则死有不足辞也。
古人有言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信矣。夫余亦以自己事卜之也。曩在嘉林时。家甚贫落。而且乡居寂寞。只得一盂饭亦幸耳。安能盛具盘上物。以侈枵然之腹欤。然于春夏之渔舶往来时。则或得小鲜而撑肠。及至秋冬。亦阙如也。朝夕之厨供。不过曰粝食粗羹。而时有鱼与肉得入膳来。则倍知其味。不识世间复有那般滋味。骄人口气也。然而此时勤苦攻业。不懈益健。惟欲着脚向前。恐有蹉跌。而不曾以温饱为忻戚。以沮其进锐之气也。夫如是。故其于业益专。而心无二歧。之东之西。又能忍其所不能忍。行其所不能行。如是推将去。自然有会意处。进步益切。盖吾心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能得内外轻重之别也。及至关外后。则大有不然者矣。官厨之礼狭。与私居自异。而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7L 页
 又其供具之馀羡。有足以及于童稚也。以是父兄为郡。则为子弟者。例享其所供之腆。而不自知其过足。有或肆其粗暴者矣。如是者。不特渠不能知其不可也。虽他人。亦或以为华。而余亦一世之人。庸能不与人同好恶而背驰也。然而夙昔之所自画。有区区不欲俯仰者。时时自厉。𥷋其一节而匪解。虽于一副当世味。常要淡泊而无累。庶几无大过。而但执志不固。是心操舍之间。率多颠错而妄动。则凡于外物之侵凌。亦安保其贞固而不惑哉。昔者王沂公初登第。刘子仪谓之曰。壮元三场。吃着不尽。公正色而语曰。曾平生意不在温饱。古人之所以用心者如是。孟子曰。食前方丈。吾得志不为也。凡今之君子不然。虽无自家气力。而亦或藉父兄馀势。慆慢自肆。惟其意欲焉。余既能诊人之病。而窃自瞿瞿。虑或有如此之行。而余未能知以是点检而思量之。则不慊于方寸者多矣。
又其供具之馀羡。有足以及于童稚也。以是父兄为郡。则为子弟者。例享其所供之腆。而不自知其过足。有或肆其粗暴者矣。如是者。不特渠不能知其不可也。虽他人。亦或以为华。而余亦一世之人。庸能不与人同好恶而背驰也。然而夙昔之所自画。有区区不欲俯仰者。时时自厉。𥷋其一节而匪解。虽于一副当世味。常要淡泊而无累。庶几无大过。而但执志不固。是心操舍之间。率多颠错而妄动。则凡于外物之侵凌。亦安保其贞固而不惑哉。昔者王沂公初登第。刘子仪谓之曰。壮元三场。吃着不尽。公正色而语曰。曾平生意不在温饱。古人之所以用心者如是。孟子曰。食前方丈。吾得志不为也。凡今之君子不然。虽无自家气力。而亦或藉父兄馀势。慆慢自肆。惟其意欲焉。余既能诊人之病。而窃自瞿瞿。虑或有如此之行。而余未能知以是点检而思量之。则不慊于方寸者多矣。余于南。犹并州也。往来周游之已久。问舍求田之有年岁矣。土地之便否。风气之异同。举皆知之。虽其常居人。亦无过余。余之违南乡而之洛之湾者。亦且五易月矣。以南州而至龙湾。地之相距不翅千有馀里。
樗村先生遗稿卷之三十七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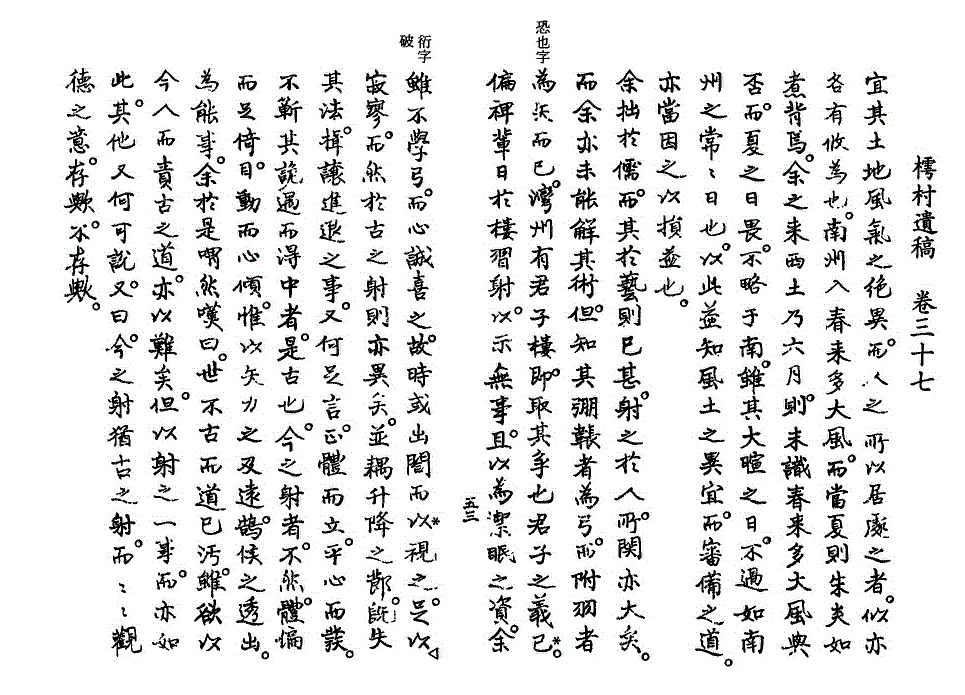 宜其土地风气之绝异。而人之所以居处之者。似亦各有攸为也。南州入春来多大风。而当夏则朱炎如煮背焉。余之来西土乃六月。则未识春来多大风与否。而夏之日畏。不略于南。虽其大暄之日。不过如南州之常常日也。以此益知风土之异宜。而审备之道。亦当因之以损益也。
宜其土地风气之绝异。而人之所以居处之者。似亦各有攸为也。南州入春来多大风。而当夏则朱炎如煮背焉。余之来西土乃六月。则未识春来多大风与否。而夏之日畏。不略于南。虽其大暄之日。不过如南州之常常日也。以此益知风土之异宜。而审备之道。亦当因之以损益也。余拙于儒。而其于艺则已甚。射之于人。所关亦大矣。而余亦未能解其术。但知其弸韔者为弓。而附羽者为矢而已。湾州有君子楼。即取其争也君子之义已(恐也字)。偏裨辈日于楼习射。以示无事。且以为御眠之资。余虽不学弓。而心诚喜之。故时或出閤而以(衍字)视之。足以破寂寥。而然于古之射则亦异矣。并耦升降之节。既失其法。揖让进退之事。又何足言。正体而立。平心而发。不𥷋其诡遇而得中者。是古也。今之射者。不然。体偏而足倚。目动而心倾。惟以矢力之及远。鹄侯之透出。为能事。余于是喟然叹曰。世不古而道已污。虽欲以今人而责古之道。亦以难矣。但以射之一事。而亦如此。其他又何可说。又曰。今之射犹古之射。而射而观德之意。存欤。不存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