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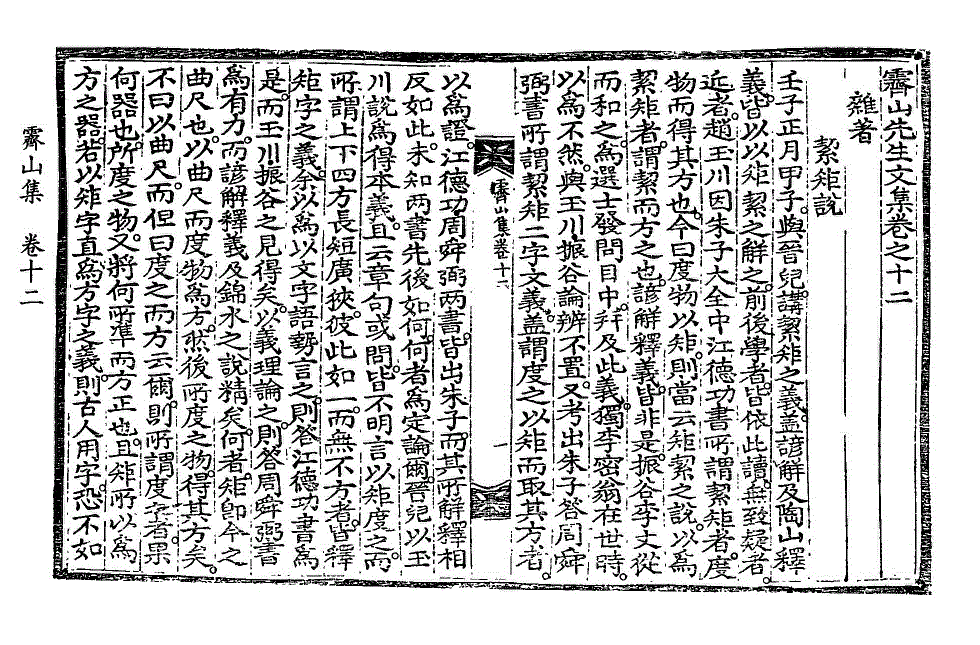 絜矩说
絜矩说壬子正月甲子。与晋儿。讲絜矩之义。盖谚解及陶山释义。皆以以矩絜之解之。前后学者。皆依此读。无致疑者。近者。赵玉川因朱子大全中江德功书所谓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今曰度物以矩。则当云矩絜之说。以为絜矩者。谓絜而方之也。谚解释义。皆非是。振谷李丈从而和之。为选士发问目中。并及此义。独李密翁在世时。以为不然。与玉川,振谷论辨不置。又考出朱子答周舜弼书所谓絜矩二字文义。盖谓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者。以为證。江德功,周舜弼两书。皆出朱子。而其所解释相反如此。未知两书先后如何。何者为定论尔。晋儿以玉川说为得本义。且云章句或问。皆不明言以矩度之。而所谓上下四方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者。皆释矩字之义。余以为以文字语势言之。则答江德功书为是。而玉川,振谷之见得矣。以义理论之。则答周舜弼书为有力。而谚解释义及锦水之说精矣。何者。矩即今之曲尺也。以曲尺而度物为方。然后所度之物。得其方矣。不曰以曲尺。而但曰度之而方云尔。则所谓度之者。果何器也。所度之物。又将何所准而方正也。且矩所以为方之器。若以矩字直为方字之义。则古人用字。恐不如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7L 页
 此之乖角。况大学文字平易明白。无一句一字艰诘者乎。然则答周舜弼书。似为晚年定论。而谚解释义及锦水之说。于义为长。姑存两说。以待异日看如何尔。
此之乖角。况大学文字平易明白。无一句一字艰诘者乎。然则答周舜弼书。似为晚年定论。而谚解释义及锦水之说。于义为长。姑存两说。以待异日看如何尔。体用说
振谷文答晋儿书中。有云凡言体用。以性情及动静言。而中庸章句。所谓费者。用之广。隐者。体之微。不可以动静论。使之思索以报。余代之下语曰。体用字。有多少般样。以动静言者。仁为体。恻隐为用之类。是也。以本末言者。忠为体。恕为用之类。是也。以微显言者。即隐为体。费为用。是也。朱子所谓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无眹为体。而其发见于事物之间者为用。即隐体费用之谓也。以此答李丈则未知李丈。以为如何尔。壬子正月己巳书。
看列子
漫看列子。至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为河曲智叟所笑。而犹不止。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而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当其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痀瘘者承蜩。其处也若橛株驹。(橛。桩也。株。木之名也。驹。定也。)执臂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此三者。皆寓言。未必实有其人与事。然余感其言。上一条。可以为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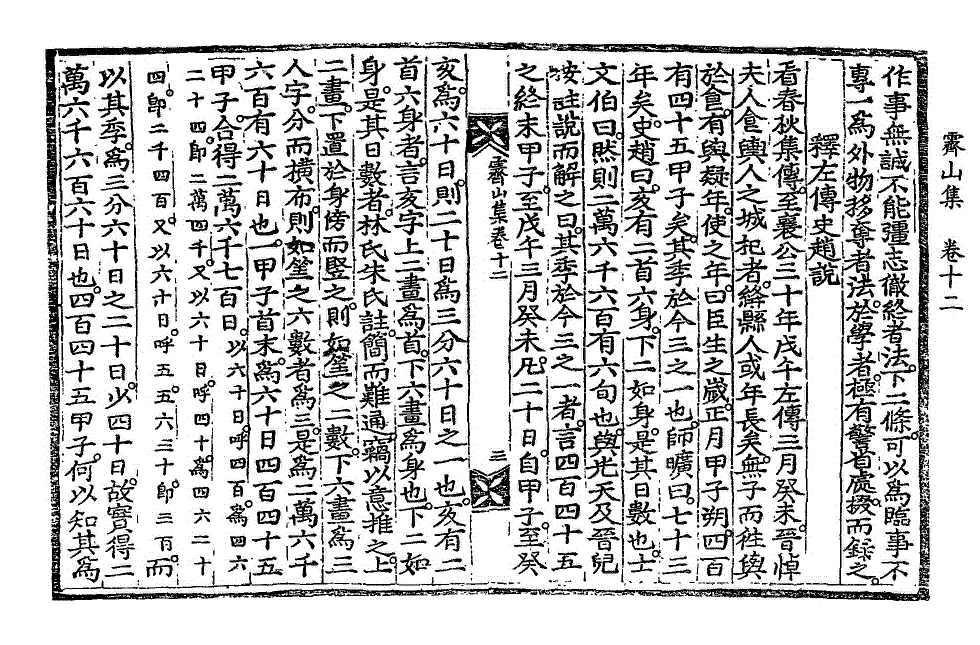 作事无诚不能彊志彻终者法。下二条。可以为临事不专一为外物移夺者法。于学者。极有警省处。掇而录之。
作事无诚不能彊志彻终者法。下二条。可以为临事不专一为外物移夺者法。于学者。极有警省处。掇而录之。释左传史赵说
看春秋集传。至襄公三十年戊午左传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师旷曰。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与光天及晋儿按注说而解之曰。其季于今三之一者。言四百四十五之终末甲子。至戊午三月癸未。凡二十日。自甲子。至癸亥。为六十日。则二十日为三分六十日之一也。亥有二首六身者。言亥字上二画为首。下六画为身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数者。林氏朱氏注。简而难通。窃以意推之。上二画。下置于身傍而竖之。则如算之二数。下六画为三人字。分而横布。则如算之六数者为三。是为二万六千六百有六十日也。一甲子首末。为六十日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万六千七百日。(以六十日。呼四百。为四六二十四。即二万四千。又以六十日。呼四十。为四六二十四。即二千四百。又以六十日。呼五。五六三十。即三百。)而以其季。为三分六十日之二十日。少四十日。故实得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四百四十五甲子。何以知其为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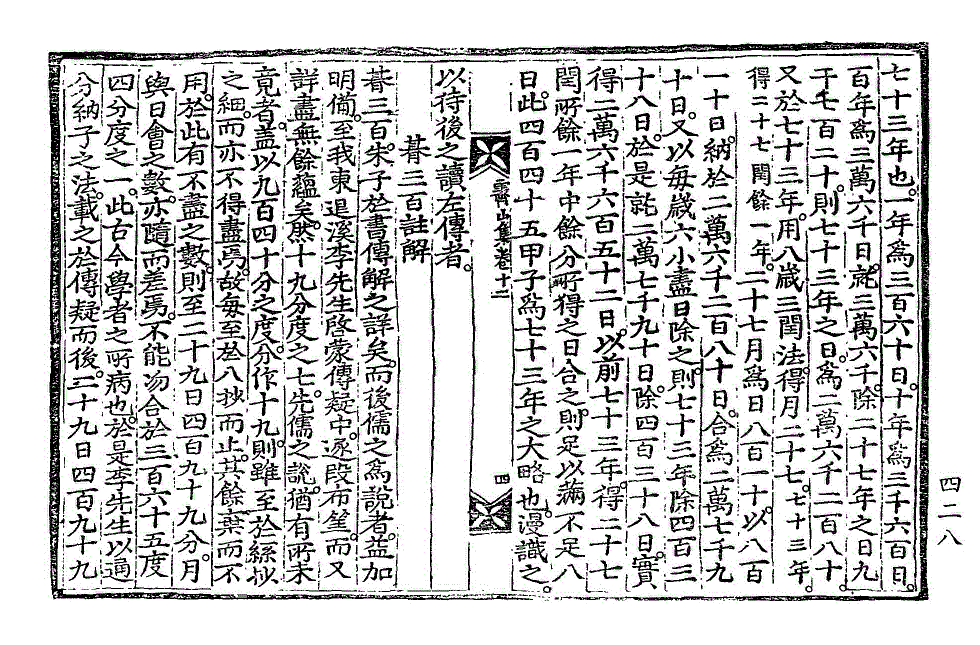 七十三年也。一年为三百六十日。十年为三千六百日。百年为三万六千日。就三万六千。除二十七年之日九千七百二十。则七十三年之日。为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又于七十三年。用八岁三闰法。得月二十七。(七十三年。得二十七闰馀一年。)二十七月为日八百一十。以八百一十日。纳于二万六千二百八十日。合为二万七千九十日。又以每岁六小尽日除之。则七十三年除四百三十八日。于是就二万七千九十日。除四百三十八日。实得二万六千六百五十二日。以前七十三年。得二十七闰所馀一年中馀分所得之日合之。则足以满不足八日。此四百四十五甲子为七十三年之大略也。漫识之。以待后之读左传者。
七十三年也。一年为三百六十日。十年为三千六百日。百年为三万六千日。就三万六千。除二十七年之日九千七百二十。则七十三年之日。为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又于七十三年。用八岁三闰法。得月二十七。(七十三年。得二十七闰馀一年。)二十七月为日八百一十。以八百一十日。纳于二万六千二百八十日。合为二万七千九十日。又以每岁六小尽日除之。则七十三年除四百三十八日。于是就二万七千九十日。除四百三十八日。实得二万六千六百五十二日。以前七十三年。得二十七闰所馀一年中馀分所得之日合之。则足以满不足八日。此四百四十五甲子为七十三年之大略也。漫识之。以待后之读左传者。期三百注解
期三百。朱子于书传解之详矣。而后儒之为说者。益加明备。至我东退溪李先生启蒙传疑中。逐段布算。而又详尽无馀蕴矣。然十九分度之七。先儒之说。犹有所未竟者。盖以九百四十分之度。分作十九。则虽至于丝抄之细。而亦不得尽焉。故每至于八抄而止。其馀弃而不用。于此有不尽之数。则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月与日会之数。亦随而差焉。不能吻合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古今学者之所病也。于是李先生以通分纳子之法。载之于传疑而后。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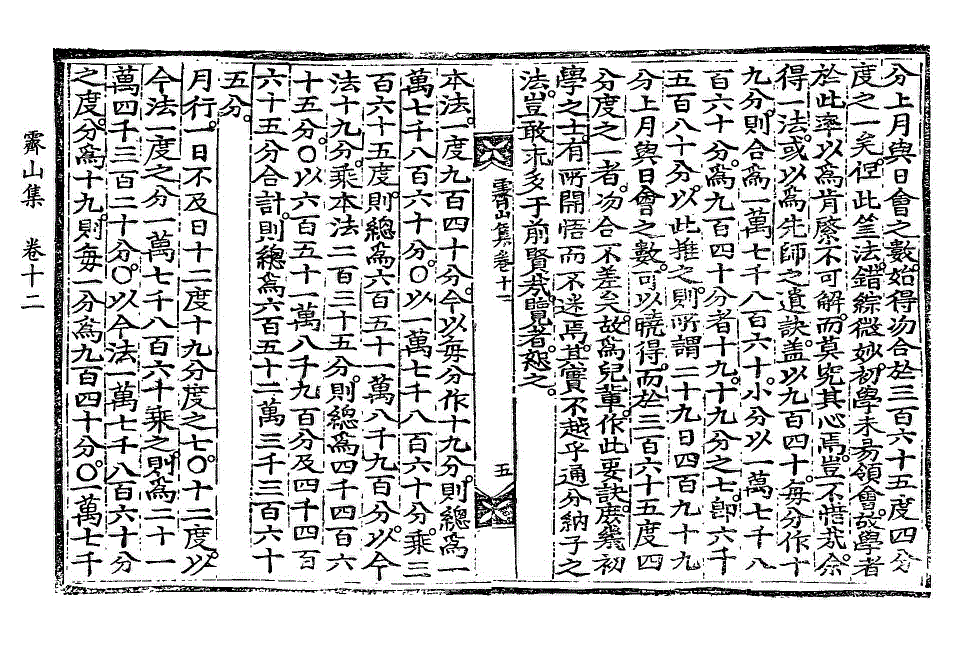 分上月与日会之数。始得吻合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矣。但此算法。错综微妙。初学未易领会。故学者于此率以为肯綮不可解。而莫究其心焉。岂不惜哉。余得一法。或以为先师之遗诀。盖以九百四十。每分作十九分。则合为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小分以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为九百四十分者十九。十九分之七。即六千五百八十分。以此推之。则所谓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月与日会之数。可以晓得。而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吻合不差矣。故为儿辈。作此要诀。庶几初学之士。有所开悟而不迷焉。其实不越乎通分纳子之法。岂敢求多于前贤哉。览者。恕之。
分上月与日会之数。始得吻合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矣。但此算法。错综微妙。初学未易领会。故学者于此率以为肯綮不可解。而莫究其心焉。岂不惜哉。余得一法。或以为先师之遗诀。盖以九百四十。每分作十九分。则合为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小分以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为九百四十分者十九。十九分之七。即六千五百八十分。以此推之。则所谓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月与日会之数。可以晓得。而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吻合不差矣。故为儿辈。作此要诀。庶几初学之士。有所开悟而不迷焉。其实不越乎通分纳子之法。岂敢求多于前贤哉。览者。恕之。本法。一度九百四十分。今以每分作十九分。则总为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以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乘三百六十五度。则总为六百五十一万八千九百分。以今法十九分。乘本法二百三十五分。则总为四千四百六十五分。○以六百五十一万八千九百分及四千四百六十五分合计。则总为六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分。
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二度。以今法一度之分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乘之。则为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分。○以今法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之度。分为十九。则每一分为九百四十分。○一万七千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L 页
 八百六十分度之内。取七个九百四十分。则总为六千五百八十分。○以六千五百八十分。纳于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分而合计之。则为二十二万口九百分。
八百六十分度之内。取七个九百四十分。则总为六千五百八十分。○以六千五百八十分。纳于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分而合计之。则为二十二万口九百分。月行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与日会。○以今法月行一日不及日之分二十二万口九百分。乘二十九日。则为六百四十口万六千一百分。○又置二十二万口九百分。以本法日分九百四十除之。则每分(即本法。日分中之一分也。)得二百三十五分。○以二百三十五分。乘四百九十九分。(亦本法日分)则为一十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五分。○以一十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五分。纳于上六百四十口万六千一百分而合计之。则总为六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分。
六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分。以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之度除之。则为三百六十五度。馀分四千四百六十五分。○四千四百六十五分。以今法十九分。作本法一分而除之。则为二百三十五分。
期三百注。肯綮难解处。最在于十九分度之七。若以一度元分九百四十分。分而为十九。则虽析至于微尘抄忽。犹有所不能尽者。十九分之析。既有所不能尽。则所谓十九之七者。安能恰得本数而无有馀不足之失哉。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日月相会之分数。亦岂能恰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无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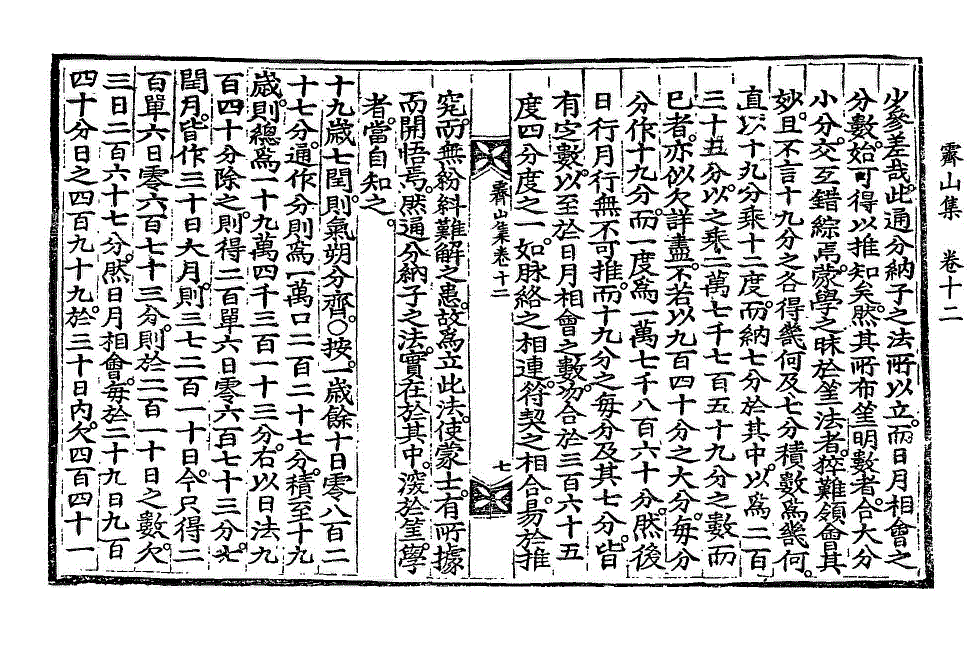 少参差哉。此通分纳子之法所以立。而日月相会之分数。始可得以推知矣。然其所布算明数者。合大分小分。交互错综焉。蒙学之昧于算法者。猝难领会其妙。且不言十九分之各得几何及七分积数为几何。直以十九分乘十二度。而纳七分于其中。以为二百三十五分。以之乘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之数而已者。亦似欠详尽。不若以九百四十分之大分。每分分作十九分。而一度为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然后日行月行无不可推。而十九分之每分及其七分。皆有定数。以至于日月相会之数。吻合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脉络之相连。符契之相合。易于推究。而无纷纠难解之患。故为立此法。使蒙士。有所据而开悟焉。然通分纳子之法。实在于其中。深于算。学者。当自知之。
少参差哉。此通分纳子之法所以立。而日月相会之分数。始可得以推知矣。然其所布算明数者。合大分小分。交互错综焉。蒙学之昧于算法者。猝难领会其妙。且不言十九分之各得几何及七分积数为几何。直以十九分乘十二度。而纳七分于其中。以为二百三十五分。以之乘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之数而已者。亦似欠详尽。不若以九百四十分之大分。每分分作十九分。而一度为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分。然后日行月行无不可推。而十九分之每分及其七分。皆有定数。以至于日月相会之数。吻合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脉络之相连。符契之相合。易于推究。而无纷纠难解之患。故为立此法。使蒙士。有所据而开悟焉。然通分纳子之法。实在于其中。深于算。学者。当自知之。十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按。一岁馀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通作分则为一万口二百二十七分。积至十九岁。则总为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右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则得二百单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七闰月。皆作三十日大月。则三七二百一十日。今只得二百单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则于二百一十日之数。欠三日二百六十七分。然日月相会。每于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于三十日内。欠四百四十一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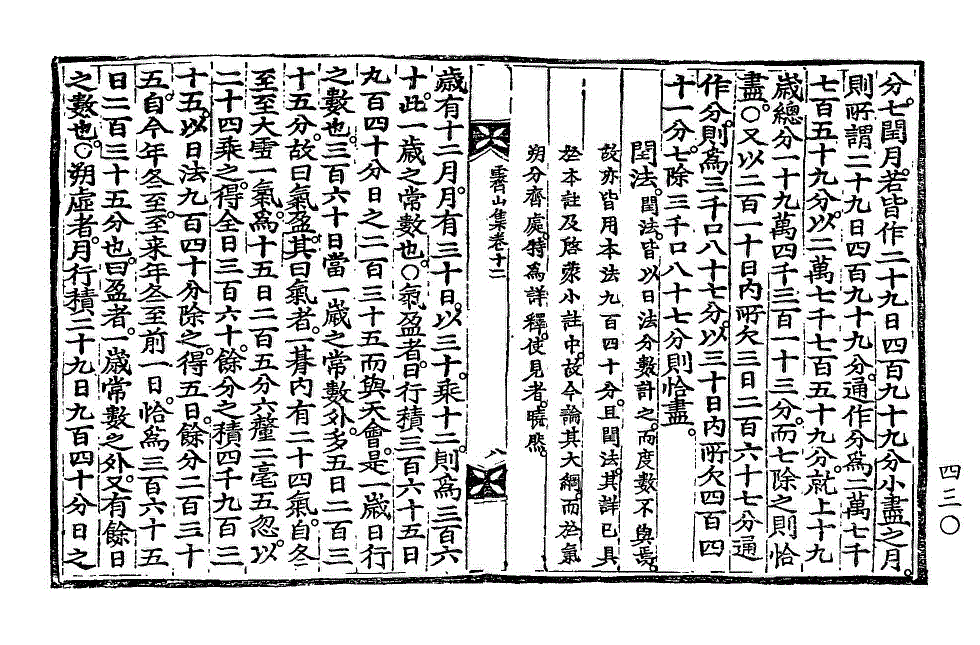 分。七闰月。若皆作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小尽之月。则所谓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通作分为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就上十九岁总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而七除之则恰尽。○又以二百一十日内所欠三日二百六十七分通作分。则为三千口八十七分。以三十日内所欠四百四十一分。七除三千口八十七分则恰尽。
分。七闰月。若皆作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小尽之月。则所谓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通作分为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就上十九岁总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而七除之则恰尽。○又以二百一十日内所欠三日二百六十七分通作分。则为三千口八十七分。以三十日内所欠四百四十一分。七除三千口八十七分则恰尽。闰法(闰法。皆以日法分数计之。而度数不与焉。故亦皆用本法九百四十分。且闰法。其详已具于本注及启蒙小注中。故今论其大纲。而于气朔分齐处。特为详释。使见者。晓然。)
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以三十。乘十二。则为三百六十。此一岁之常数也。○气盈者。日行积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与天会。是一岁日行之数也。三百六十日当一岁之常数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故曰气盈。其曰气者。一期内有二十四气。自冬至至大雪一气。为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二毫五忽。以二十四乘之。得全日三百六十。馀分之积四千九百三十五。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五日。馀分二百三十五。自今年冬至。至来年冬至前一日。恰为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也。曰盈者。一岁常数之外。又有馀日之数也。○朔虚者。月行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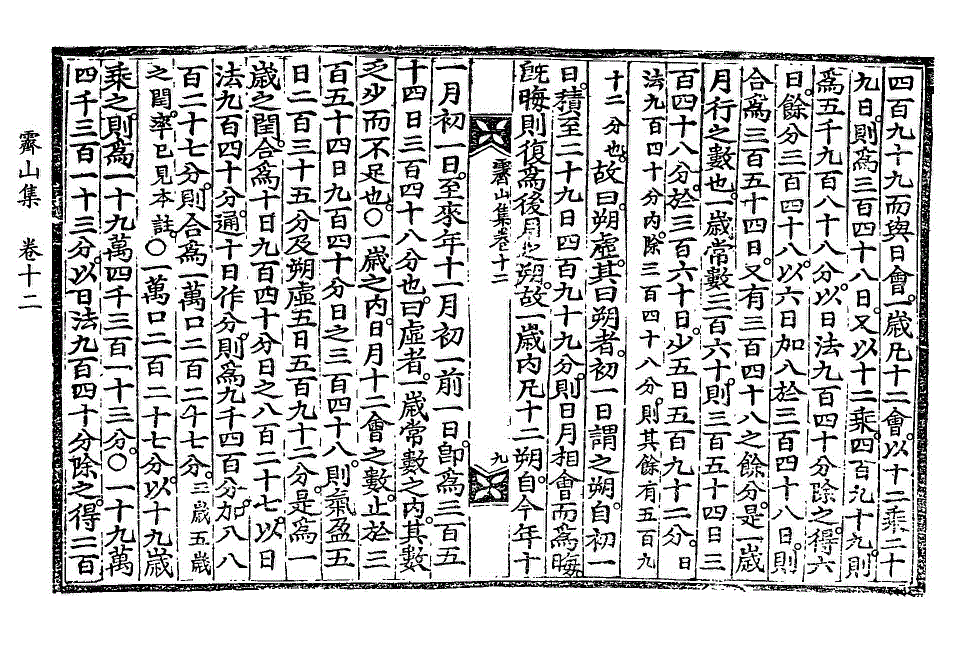 四百九十九而与日会。一岁凡十二会。以十二乘二十九日。则为三百四十八日。又以十二乘。四百九十九。则为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馀分三百四十八。以六日加入于三百四十八日。则合为三百五十四日。又有三百四十八之馀分。是一岁月行之数也。一岁常数三百六十。则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于三百六十日。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日法九百四十分内。除三百四十八分。则其馀有五百九十二分也。)故曰。朔虚。其曰朔者。初一日谓之朔。自初一日。积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则日月相会而为晦。既晦则复为后月之朔。故一岁内凡十二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日。至来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即为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也。曰虚者。一岁常数之内。其数乏少而不足也。○一岁之内。日月十二会之数。止于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则气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及朔虚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是为一岁之闰。合为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十日作分。则为九千四百分。加入八百二十七分。则合为一万口二百二十七分。(三岁五岁之闰。率已见本注。)○一万口二百二十七分。以十九岁乘之。则为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二百
四百九十九而与日会。一岁凡十二会。以十二乘二十九日。则为三百四十八日。又以十二乘。四百九十九。则为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馀分三百四十八。以六日加入于三百四十八日。则合为三百五十四日。又有三百四十八之馀分。是一岁月行之数也。一岁常数三百六十。则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于三百六十日。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日法九百四十分内。除三百四十八分。则其馀有五百九十二分也。)故曰。朔虚。其曰朔者。初一日谓之朔。自初一日。积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则日月相会而为晦。既晦则复为后月之朔。故一岁内凡十二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日。至来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即为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也。曰虚者。一岁常数之内。其数乏少而不足也。○一岁之内。日月十二会之数。止于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则气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及朔虚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是为一岁之闰。合为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十日作分。则为九千四百分。加入八百二十七分。则合为一万口二百二十七分。(三岁五岁之闰。率已见本注。)○一万口二百二十七分。以十九岁乘之。则为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二百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L 页
 单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以二百单六日及六百七十三分。作三十日大月。则为六个月及二十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于七闰月之数。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若以二百单六日及六百七十三分。作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与日会之数。)小尽之月。则七个二十九日为二百单三日。于二百单六日内。除此二百三日。则馀三日。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三日作分。则为二千八百二十分。并上六百七十三分。为三千四百九十三分。以七个四百九十九分。(七个四百九十九分。即为三千四百九十三分。)除之则恰尽。于是气盈朔虚之数。无有馀不足之分。故曰分齐。是为一章也。○又法二十九日。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之。并四百九十九分。则为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此七除十九岁积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则恰尽。
单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以二百单六日及六百七十三分。作三十日大月。则为六个月及二十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于七闰月之数。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若以二百单六日及六百七十三分。作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与日会之数。)小尽之月。则七个二十九日为二百单三日。于二百单六日内。除此二百三日。则馀三日。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三日作分。则为二千八百二十分。并上六百七十三分。为三千四百九十三分。以七个四百九十九分。(七个四百九十九分。即为三千四百九十三分。)除之则恰尽。于是气盈朔虚之数。无有馀不足之分。故曰分齐。是为一章也。○又法二十九日。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通之。并四百九十九分。则为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此七除十九岁积分一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三分则恰尽。晋儿启蒙质疑辨
第一条勉斋说
天地奇偶始终之数。不过自一至十。而五行之生成。亦各一奇一偶而已。以奇生者。以偶成之。以偶生者。以奇成之。五奇五偶。合而为十。故以十数中分之。自五以前。为五行之生数。自六以后。为五行之成数。而其生其成。非判然两截事。天一生水之际。地六之成数已具。地二生火之际。天七之成数已具。汝之所谓一才生水。六便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H 页
 成之。二才生火。七便成之。混然妙合。初无隔截先后之分者。是也。勉斋所谓一生水而未成。必至五行俱生而后。待第六而方成水。则全不成造化云者。恐疑之太过耳。但汝之所为说。亦有一二处未稳者。若于则不过五而已之下。去故初五以下二十五字。相对以成十下去初非以下二十八字。则语意无不足。而亦不使人致疑矣。又于五才生土十便成之之下。去水之成以下七十字。而直接于而其生其成之句。则指意简洁而无丛杂之病矣。如何如何。盖所谓初五之后六又为一。七又为二云者。意虽可通。而语涉可骇。至于所谓水之成虽曰六。其实一之偶成之也等语。虽似略有意思。而未免不成说故云尔。若夫奇偶多寡之数。吾有一说焉。盖从一二而数之。以至于十。则多寡固有分矣。然河图之数以中五为本。故一得五而为六。数止于六。二得五而为七。而一数既为水所占。则自二至七。亦止于六。一与二既为水火所占。则三得五而为八。而自三至八。亦为六矣。一与二三。为水火木之所占。则四得五而为九。而自四至九。亦为六矣。一二三四为水火木金之所占。则五得五而为十。而自五至十亦不过六而已。然则自一至十之数。虽有多寡之殊。而五行生成之数。皆不过六。未见有饶乏不齐之象矣。此虽未稽于先儒之说。而亦或可备一义耶。偶见如此。未知汝意如何。五行生出次第。不
成之。二才生火。七便成之。混然妙合。初无隔截先后之分者。是也。勉斋所谓一生水而未成。必至五行俱生而后。待第六而方成水。则全不成造化云者。恐疑之太过耳。但汝之所为说。亦有一二处未稳者。若于则不过五而已之下。去故初五以下二十五字。相对以成十下去初非以下二十八字。则语意无不足。而亦不使人致疑矣。又于五才生土十便成之之下。去水之成以下七十字。而直接于而其生其成之句。则指意简洁而无丛杂之病矣。如何如何。盖所谓初五之后六又为一。七又为二云者。意虽可通。而语涉可骇。至于所谓水之成虽曰六。其实一之偶成之也等语。虽似略有意思。而未免不成说故云尔。若夫奇偶多寡之数。吾有一说焉。盖从一二而数之。以至于十。则多寡固有分矣。然河图之数以中五为本。故一得五而为六。数止于六。二得五而为七。而一数既为水所占。则自二至七。亦止于六。一与二既为水火所占。则三得五而为八。而自三至八。亦为六矣。一与二三。为水火木之所占。则四得五而为九。而自四至九。亦为六矣。一二三四为水火木金之所占。则五得五而为十。而自五至十亦不过六而已。然则自一至十之数。虽有多寡之殊。而五行生成之数。皆不过六。未见有饶乏不齐之象矣。此虽未稽于先儒之说。而亦或可备一义耶。偶见如此。未知汝意如何。五行生出次第。不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L 页
 但有朱子定论。勉斋他说。亦有如此者。恐不可复容他议矣。
但有朱子定论。勉斋他说。亦有如此者。恐不可复容他议矣。第二条。帝出乎震章。胡玉斋说。
先天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而乾坤之交。则坤上乾下。而各反其所自生。所谓乾生于子。坤生于午者。先天图。一阳之复生于子半。而进至于午。则为纯阳之乾。一阴之垢生于午半。而进至于子。则为纯阴之坤。坎离之交。则坎东离西。而各变其所居之位。所谓坎终于寅。离终于申者。先天图。水火既济。当寅之半。火水未济。当申之半。此皆先天卦气之相交。而变而无定位者。故邵子以为应天之时。而胡氏之以先天当之者。以此欤。及其再变。然后乾自北而退居乎西北。坤自南而退居乎西南。坎自东而下居乎北。离自西而上居乎南。乾坤既居不用之地。则震居于东。而主发生。犹长子代父而用事也。巽居于东南。而主长养。犹长女代母而用事也。艮以少男居东北。而终万物始万物。兑以少女居正西。而主成物。盖坎离震兑各居四方之正位。乾坤各居无用之地。而无交变之象。故为后天。而邵子以为应地之方也欤。又按乾坤之交而为奉。坎离之交而为既济。盖自先天而为后天之渐也。胡氏之以此专属先天者。虽若可疑。而亦不可非斥之也。如何如何。
第三条明蓍策篇。胡氏径围说。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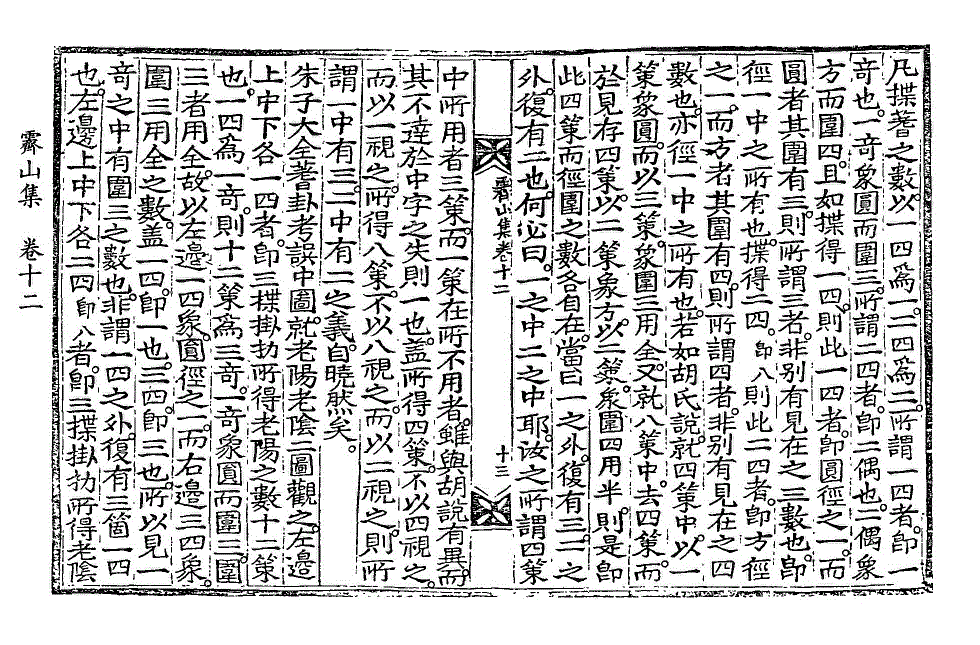 凡揲蓍之数。以一四为一。二四为二。所谓一四者。即一奇也。一奇象圆而围三。所谓二四者。即二偶也。二偶象方而围四。且如揲得一四。则此一四者。即圆径之一。而圆者其围有三。则所谓三者。非别有见在之三数也。即径一中之所有也。揲得二四。(即八。)则此二四者。即方径之一。而方者其围有四。则所谓四者。非别有见在之四数也。亦径一中之所有也。若如胡氏说。就四策中。以一策象圆。而以三策。象围三用全。又就八策中。去四策。而于见存四策。以二策象方。以二策。象围四用半。则是即此四策而径围之数各自在。当曰一之外。复有三。二之外。复有二也。何必曰。一之中二之中耶。汝之所谓四策中所用者三策。而一策在所不用者。虽与胡说有异。而其不达于中字之失则一也。盖所得四策。不以四视之。而以一视之。所得八策。不以八视之。而以二视之。则所谓一中有三。二中有二之义。自晓然矣。
凡揲蓍之数。以一四为一。二四为二。所谓一四者。即一奇也。一奇象圆而围三。所谓二四者。即二偶也。二偶象方而围四。且如揲得一四。则此一四者。即圆径之一。而圆者其围有三。则所谓三者。非别有见在之三数也。即径一中之所有也。揲得二四。(即八。)则此二四者。即方径之一。而方者其围有四。则所谓四者。非别有见在之四数也。亦径一中之所有也。若如胡氏说。就四策中。以一策象圆。而以三策。象围三用全。又就八策中。去四策。而于见存四策。以二策象方。以二策。象围四用半。则是即此四策而径围之数各自在。当曰一之外。复有三。二之外。复有二也。何必曰。一之中二之中耶。汝之所谓四策中所用者三策。而一策在所不用者。虽与胡说有异。而其不达于中字之失则一也。盖所得四策。不以四视之。而以一视之。所得八策。不以八视之。而以二视之。则所谓一中有三。二中有二之义。自晓然矣。朱子大全蓍卦考误中图。就老阳老阴二图观之。左边上中下各一四者。即三揲挂扐所得老阳之数十二策也。一四为一奇。则十二策为三奇。一奇象圆而围三。围三者用全。故以左边一四象。圆径之一。而右边三四象。围三用全之数。盖一四。即一也。三四。即三也。所以见一奇之中有围三之数也。非谓一四之外。复有三个一四也。左边上中下各二四(即八)者。即三揲挂扐所得老阴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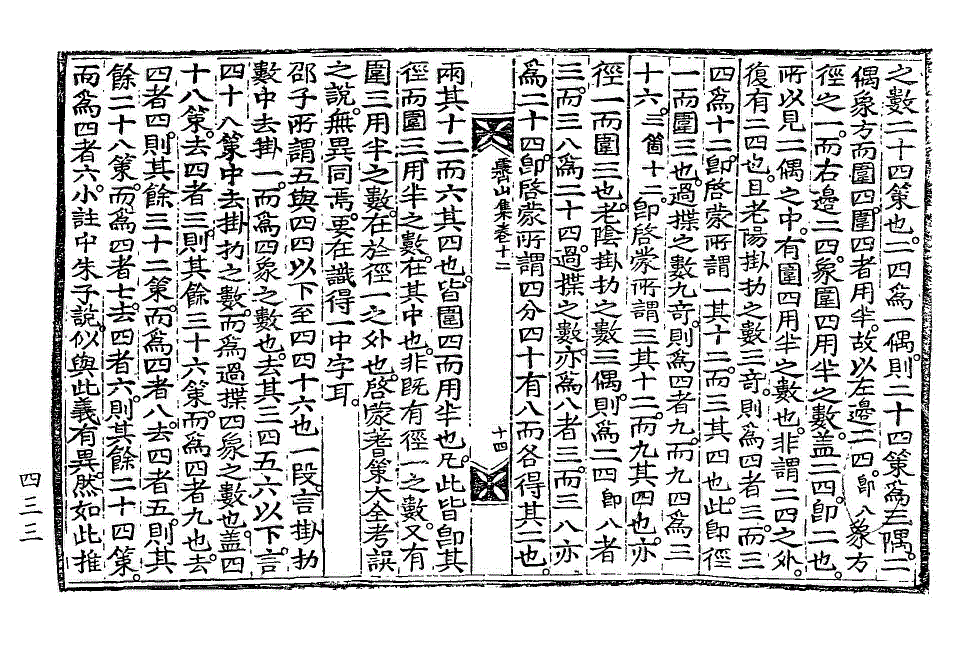 之数二十四策也。二四为一偶。则二十四策为三隅。二偶象方而围四。围四者用半。故以左边二四。(即八。)象方径之一。而右边二四。象围四用半之数。盖二四。即二也。所以见二偶之中。有围四用半之数也。非谓二四之外。复有二四也。且老阳挂扐之数三奇。则为四者三。而三四为十二。即启蒙所谓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此即径一而围三也。过揲之数九奇。则为四者九。而九四为三十六。(三个十二。)即启蒙所谓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亦径一而围三也。老阴挂扐之数三偶。则为二四(即八)者三。而三八为二十四。过揲之数。亦为八者三。而三八亦为二十四。即启蒙所谓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两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围四而用半也。凡此皆即其径而围三用半之数。在其中也。非既有径一之数。又有围三用半之数。在于径一之外也。启蒙蓍策大全考误之说。无异同焉。要在识得一中字耳。
之数二十四策也。二四为一偶。则二十四策为三隅。二偶象方而围四。围四者用半。故以左边二四。(即八。)象方径之一。而右边二四。象围四用半之数。盖二四。即二也。所以见二偶之中。有围四用半之数也。非谓二四之外。复有二四也。且老阳挂扐之数三奇。则为四者三。而三四为十二。即启蒙所谓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此即径一而围三也。过揲之数九奇。则为四者九。而九四为三十六。(三个十二。)即启蒙所谓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亦径一而围三也。老阴挂扐之数三偶。则为二四(即八)者三。而三八为二十四。过揲之数。亦为八者三。而三八亦为二十四。即启蒙所谓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两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围四而用半也。凡此皆即其径而围三用半之数。在其中也。非既有径一之数。又有围三用半之数。在于径一之外也。启蒙蓍策大全考误之说。无异同焉。要在识得一中字耳。邵子所谓五与四四以下至四四十六也一段。言挂扐数中去挂一。而为四象之数也。去其三四五六以下。言四十八策中去挂扐之数。而为过揲四象之数也。盖四十八策。去四者三。则其馀三十六策。而为四者九也。去四者四。则其馀三十二策。而为四者八。去四者五。则其馀二十八策。而为四者七。去四者六。则其馀二十四策。而为四者六。小注中朱子说。似与此义有异。然如此推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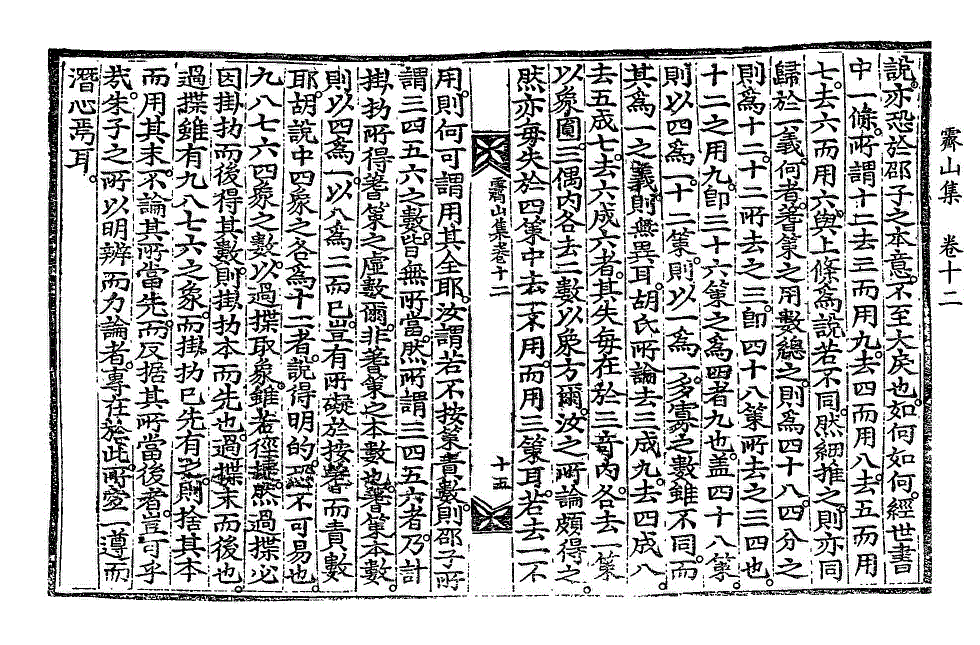 说。亦恐于邵子之本意。不至大戾也。如何如何。经世书中一条。所谓十二去三而用九。去四而用八。去五而用七。去六而用六。与上条为说若不同。然细推之。则亦同归于一义。何者。蓍策之用数总之。则为四十八。四分之则为十二。十二所去之三。即四十八策所去之三四也。十二之用九。即三十六策之为四者九也。盖四十八策。则以四为一。十二策。则以一为一。多寡之数虽不同。而其为一之义。则无异耳。胡氏所论去三成九。去四成八。去五成七。去六成六者。其失每在于三奇内。各去一策以象圆。三偶内各去二数以象方尔。汝之所论颇得之。然亦每失于四策中去一不用。而用三策耳。若去一不用。则何可谓用其全耶。汝谓若不按策责数。则邵子所谓三四五六之数。皆无所当。然所谓三四五六者。乃计挂扐所得蓍策之虚数尔。非蓍策之本数也。蓍策本数。则以四为一。以八为二而已。岂有所碍于按蓍而责数耶。胡说中四象之各为十二者。说得明的。恐不可易也。九八七六四象之数。以过揲取象。虽若径捷。然过揲必因挂扐而后得其数。则挂扐本而先也。过揲末而后也。过揲虽有九八七六之象。而挂扐已先有之。则舍其本而用其末。不论其所当先。而反据其所当后者。岂可乎哉。朱子之所以明辨而力论者。专在于此。所宜一遵而潜心焉耳。
说。亦恐于邵子之本意。不至大戾也。如何如何。经世书中一条。所谓十二去三而用九。去四而用八。去五而用七。去六而用六。与上条为说若不同。然细推之。则亦同归于一义。何者。蓍策之用数总之。则为四十八。四分之则为十二。十二所去之三。即四十八策所去之三四也。十二之用九。即三十六策之为四者九也。盖四十八策。则以四为一。十二策。则以一为一。多寡之数虽不同。而其为一之义。则无异耳。胡氏所论去三成九。去四成八。去五成七。去六成六者。其失每在于三奇内。各去一策以象圆。三偶内各去二数以象方尔。汝之所论颇得之。然亦每失于四策中去一不用。而用三策耳。若去一不用。则何可谓用其全耶。汝谓若不按策责数。则邵子所谓三四五六之数。皆无所当。然所谓三四五六者。乃计挂扐所得蓍策之虚数尔。非蓍策之本数也。蓍策本数。则以四为一。以八为二而已。岂有所碍于按蓍而责数耶。胡说中四象之各为十二者。说得明的。恐不可易也。九八七六四象之数。以过揲取象。虽若径捷。然过揲必因挂扐而后得其数。则挂扐本而先也。过揲末而后也。过揲虽有九八七六之象。而挂扐已先有之。则舍其本而用其末。不论其所当先。而反据其所当后者。岂可乎哉。朱子之所以明辨而力论者。专在于此。所宜一遵而潜心焉耳。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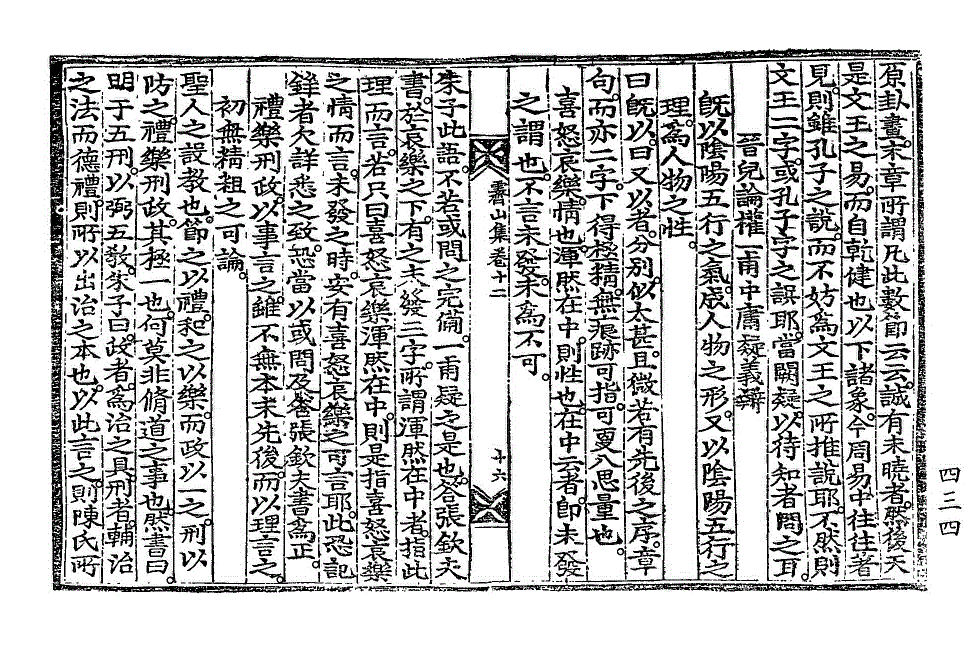 原卦画。末章所谓凡此数节云云。诚有未晓者。然后天是文王之易。而自乾健也以下诸象。今周易中往往著见。则虽孔子之说。而不妨为文王之所推说耶。不然则文王二字。或孔子字之误耶。当阙疑。以待知者问之耳。
原卦画。末章所谓凡此数节云云。诚有未晓者。然后天是文王之易。而自乾健也以下诸象。今周易中往往著见。则虽孔子之说。而不妨为文王之所推说耶。不然则文王二字。或孔子字之误耶。当阙疑。以待知者问之耳。晋儿论权一甫中庸疑义辨
既以阴阳五行之气。成人物之形。又以阴阳五行之理。为人物之性。
曰既以。曰又以者。分别。似太甚。且微若有先后之序。章句。而亦二字。下得极精。无痕迹可指。可更入思量也。
喜怒哀乐。情也。浑然在中。则性也。在中云者。即未发之谓也。不言未发。未为不可。
朱子此语。不若或问之完备。一甫疑之是也。答张钦夫书。于哀乐之下。有之未发三字。所谓浑然在中者。指此理而言。若只曰喜怒哀乐浑然在中。则是指喜怒哀乐之情而言。未发之时。安有喜怒哀乐之可言耶。此恐记录者欠详悉之致。恐当以或问及答张钦夫书为正。
礼乐刑政。以事言之。虽不无本末先后。而以理言之。初无精粗之可论。
圣人之设教也。节之以礼。和之以乐。而政以一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何莫非脩道之事也。然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朱子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而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也。以此言之。则陈氏所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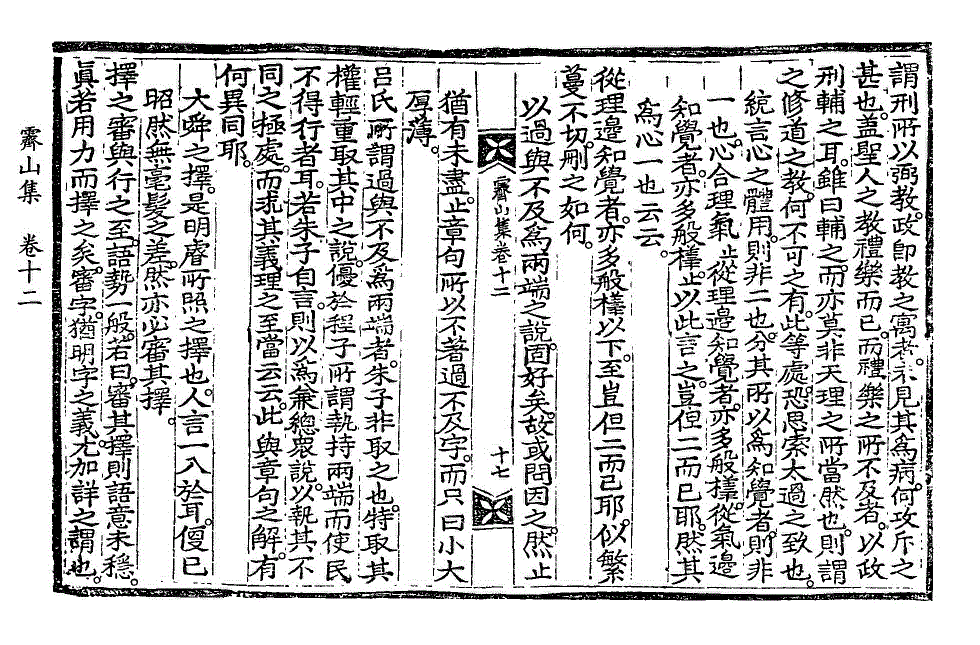 谓刑所以弼教。政即教之寓者。未见其为病。何攻斥之甚也。盖圣人之教礼乐而已。而礼乐之所不及者。以政刑辅之耳。虽曰辅之。而亦莫非天理之所当然也。则谓之修道之教。何不可之有。此等处。恐思索太过之致也。
谓刑所以弼教。政即教之寓者。未见其为病。何攻斥之甚也。盖圣人之教礼乐而已。而礼乐之所不及者。以政刑辅之耳。虽曰辅之。而亦莫非天理之所当然也。则谓之修道之教。何不可之有。此等处。恐思索太过之致也。统言心之体用。则非二也。分其所以为知觉者。则非一也。心合理气(止)从理边知觉者。亦多般样。从气边知觉者。亦多般样。(止)以此言之。岂但二而已耶。然其为心一也云云。
从理边知觉者。亦多般样以下。至岂但二而已耶。似繁蔓不切。删之如何。
以过与不及为两端之说。固好矣。故或问因之。然(止)犹有未尽。(止)章句所以不著过不及字。而只曰小大厚薄。
吕氏所谓过与不及为两端者。朱子非取之也。特取其权轻重取其中之说。优于程子所谓执持两端而使民不得行者耳。若朱子自言。则以为兼总众说。以执其不同之极处。而求其义理之至当云云。此与章句之解。有何异同耶。
大舜之择。是明睿所照之择也。人言一入于耳。便已昭然无毫发之差。然亦必审其择。
择之审与行之至。语势一般。若曰。审其择则语意未稳。真若用力而择之矣。审字。犹明字之义。尤加详之谓也。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L 页
 五常三德。必欲分配。则五常之信。可拟三德之勇。
五常三德。必欲分配。则五常之信。可拟三德之勇。第二十章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也。诚者。信也。则五常之信。恐不可拟于勇。而其下文曰。知耻近乎勇。耻即羞恶之谓也。一甫所谓义近于勇者。或似之。然此等处。本不必强求配合。朱子于学者。如此牵强分属处。辄痛斥之。后学。何敢复犯此戒耶。吾意勇虽性之德。与五常之为纯理者。微有不同。试思之。
援非独附托求取之意。如下官不肯逊屈于上官之类。亦不害为援。
在下者。不肯尽礼于在上之人。亦为援上者。果有所考据否。其所以为援之义。吾未知之也。
若就盛论言之。乐字于顺字。似低却一位。而乃云侵过何也。
顺与安乐字。有何分别。一甫侵过之说及汝之所谓低一位者。皆吾所未能知也。
所谓祭祀之鬼神。非独言人鬼。阴阳造化。便是神祇。(止)如陈氏说。则阴阳屈伸。自是一般鬼神。所祭祀者。又是一般鬼神。恐无是理。
天地间。造化之屈伸往来进退消息荣悴开落死生终始。皆鬼神也。故此章首言鬼神之无所不包。而下又特言祭祀之鬼神。明体物不遗之验。陈氏说得此一节之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H 页
 意。未见其有差。且其意非以阴阳屈伸为一般鬼神。使人祭祀者。为一般鬼神。其所谓无所不包之中拈出云云者。语意的当。谓之无是理者。何也。此亦思索之过也。
意。未见其有差。且其意非以阴阳屈伸为一般鬼神。使人祭祀者。为一般鬼神。其所谓无所不包之中拈出云云者。语意的当。谓之无是理者。何也。此亦思索之过也。都宫。以别有门垣之语观之。恐非绕以周垣者。似是合群庙而言者也。盖内虽各有寝庙。而外实统同周匝。故谓之都宫。都宫之外。乃设门垣。未知是否。
天子七庙。庙各自有门垣。而七庙之外。又有一大垣门。以周匝之。则都宫之名。因此而得之。今曰都宫之外。乃设门垣。未知于文义如何。若以其统同周匝。而谓之都宫。则所谓外为二字。有不通矣。更详之。
士大夫家。有不迁主者。沙溪,旅轩所论不同。不知何所适从。
天子七庙。世室不在常数中。则士夫家不迁主。亦不当并数于祭四代之数矣。以沙,旅说。论之。恐旅轩说。为长。
童蒙学令
凡童子之行。务恭谨。戒轻俊。禁傲惰。
侍长者。毋敢哗。毋敢怠。坐必隅。行必随。命之事。则奉行惟谨。召之。应唯即至无敢稽。有问敬对。语必辨。长者出入。必作。长者出外经宿以上。则拜送于外户外。及归。亦出外户而迎拜。凡父兄尊客之来归。皆如之。长者所坐之处。毋敢居。长者书册器用。毋敢动。非长者所命。毋敢擅为。凡有所为。必请而后行。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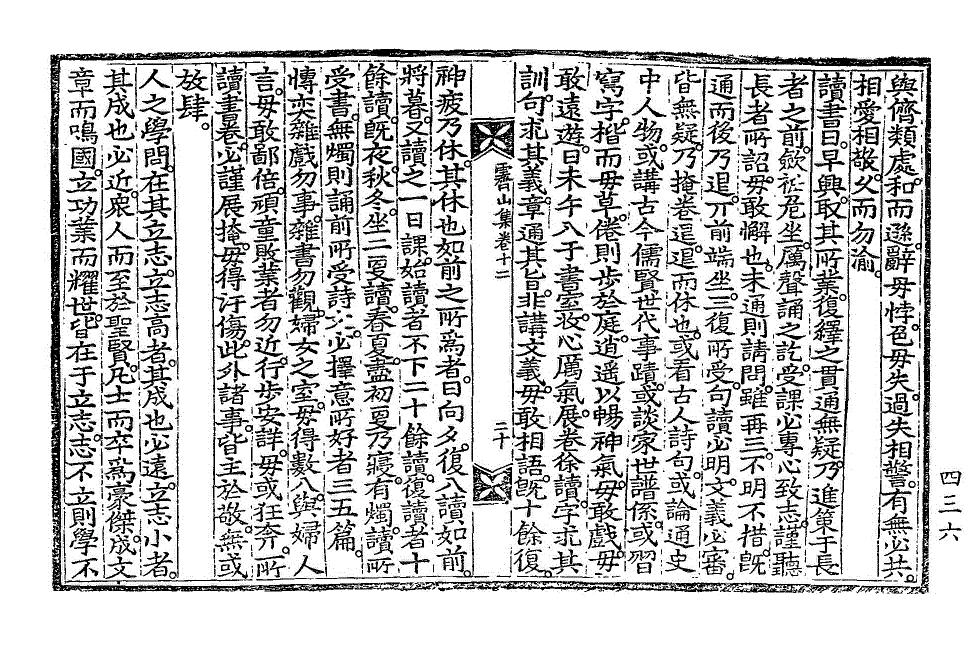 与侪类处。和而逊。辞毋悖。色毋失。过失相警。有无必共。相爱相敬。久而勿渝。
与侪类处。和而逊。辞毋悖。色毋失。过失相警。有无必共。相爱相敬。久而勿渝。读书日。早兴。取其所业。复绎之贯通无疑。乃进策于长者之前。敛衽危坐。厉声诵之讫。受课必专心致志。谨听长者所诏。毋敢懈也。未通则请问。虽再三。不明不措。既通而后乃退。丌前端坐。三复所受。句读必明。文义必审。皆无疑。乃掩卷退。退而休也。或看古人诗句。或论通史中人物。或讲古今儒贤世代事迹。或谈家世谱系。或习写字。楷而毋草。倦则步于庭。逍遥以畅神气。毋敢戏。毋敢远游。日未午入于书室。收心厉气。展卷徐读。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通其旨。非讲文义。毋敢相语。既十馀复。神疲乃休。其休也如前之所为者。日向夕。复入读如前。将暮。又读之一日课。始读者不下二十馀读。复读者十馀读。既夜。秋冬。坐二更读。春夏。尽初更乃寝。有烛。读所受书。无烛则诵前所受诗文。必择意所好者三五篇。
博奕杂戏勿事。杂书勿观。妇女之室。毋得数入。与妇人言。毋敢鄙倍。顽童败业者勿近。行步安详。毋或狂奔。所读书卷。必谨展掩。毋得污伤。此外诸事。皆主于敬。无或放肆。
人之学问。在其立志。立志高者。其成也必远。立志小者。其成也必近。众人而至于圣贤。凡士而卒为豪杰。成文章而鸣国。立功业而耀世。皆在于立志。志不立则学不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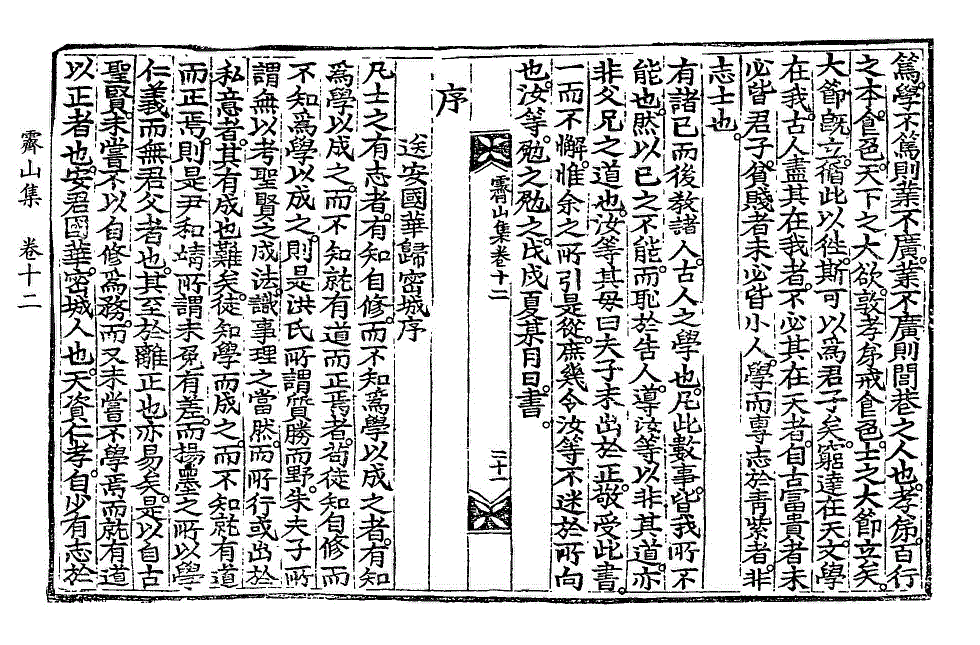 笃。学不笃则业不广。业不广则闾巷之人也。孝弟。百行之本。食色。天下之大欲。敦孝弟戒食色。士之大节立矣。大节既立。循此以往。斯可以为君子矣。穷达在天。文学在我。古人尽其在我者。不必其在天者。自古富贵者未必皆君子。贫贱者未必皆小人。学而专志于青紫者。非志士也。
笃。学不笃则业不广。业不广则闾巷之人也。孝弟。百行之本。食色。天下之大欲。敦孝弟戒食色。士之大节立矣。大节既立。循此以往。斯可以为君子矣。穷达在天。文学在我。古人尽其在我者。不必其在天者。自古富贵者未必皆君子。贫贱者未必皆小人。学而专志于青紫者。非志士也。有诸己而后教诸人。古人之学也。凡此数事。皆我所不能也。然以己之不能。而耻于告人。导汝等以非其道。亦非父兄之道也。汝等其毋曰夫子未出于正。敬受此书。一而不懈。惟余之所引是从。庶几令汝等不迷于所向也。汝等。勉之勉之。戊戌夏某月日。书。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安国华归密城序
凡士之有志者。有知自修。而不知为学以成之者。有知为学以成之。而不知就有道而正焉者。苟徒知自修而不知为学以成之。则是洪氏所谓质胜而野。朱夫子所谓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者。其有成也难矣。徒知学而成之。而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则是尹和靖所谓未免有差。而扬,墨之所以学仁义而无君父者也。其至于离正也亦易矣。是以自古圣贤。未尝不以自修为务。而又未尝不学焉而就有道以正者也。安君国华。密城人也。天资仁孝。自少有志于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L 页
 学。每病世之为学者。徒以科第为贵。而文辞为贤。能自力修身。旁读书史。而以未得贤师友而从游为恨矣。粤在己卯。闻我先生蒙 天恩。自北而南。乃私自欣然趋拜于其门。承诲出入者盖有日矣。去年春。先生放归于此地。与远近学者讲道。安君又不远数百里。负笈来谒。自春及夏。受业不怠。若君者。真可谓能自修而知为学。能为学而知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今者君之来已过三月。而乡音疏矣。定省旷矣。君不禁北堂之思。乃告于先生别侪友。而旋归于密城。余送之江头。执手而言曰。君归养萱闱。情之喜者也。远离丈席。情之悲者也。其喜其悲。皆情之当也。而吾于君。有所恨焉。昔陈仲举有言曰。旬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仲举贤人也。旬月不久也。犹有此叹。况如我之愚鲁。不敢比古人之万一。自此日之别。与君不相见。将涉几旬月也。而鄙吝之萌于心。将不知其几何也耶。嗟乎。惜别之怀。言之无益。惟愿君从此以往。益孳孳勉力。其于捡身饬行。固不容少懈。而学问思辨之功。亦不可使间断也。是乃先生之所尝语君者。而君之所亲承者也。君其服膺勿失。惟日不足。上不负先生之训诲。下以副吾侪之所望也。相爱之至。敢以此告之。诚知其不自量也。惟君不以人观言。勖哉勉哉。辛巳清和下浣。同门友金圣铎。序。
学。每病世之为学者。徒以科第为贵。而文辞为贤。能自力修身。旁读书史。而以未得贤师友而从游为恨矣。粤在己卯。闻我先生蒙 天恩。自北而南。乃私自欣然趋拜于其门。承诲出入者盖有日矣。去年春。先生放归于此地。与远近学者讲道。安君又不远数百里。负笈来谒。自春及夏。受业不怠。若君者。真可谓能自修而知为学。能为学而知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今者君之来已过三月。而乡音疏矣。定省旷矣。君不禁北堂之思。乃告于先生别侪友。而旋归于密城。余送之江头。执手而言曰。君归养萱闱。情之喜者也。远离丈席。情之悲者也。其喜其悲。皆情之当也。而吾于君。有所恨焉。昔陈仲举有言曰。旬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仲举贤人也。旬月不久也。犹有此叹。况如我之愚鲁。不敢比古人之万一。自此日之别。与君不相见。将涉几旬月也。而鄙吝之萌于心。将不知其几何也耶。嗟乎。惜别之怀。言之无益。惟愿君从此以往。益孳孳勉力。其于捡身饬行。固不容少懈。而学问思辨之功。亦不可使间断也。是乃先生之所尝语君者。而君之所亲承者也。君其服膺勿失。惟日不足。上不负先生之训诲。下以副吾侪之所望也。相爱之至。敢以此告之。诚知其不自量也。惟君不以人观言。勖哉勉哉。辛巳清和下浣。同门友金圣铎。序。随见杂录序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H 页
 士以书为业。天下之书。无不该通而后。可以称士之名。而书籍浩漫。不可以随编烂读。于是乎有记览之工焉。然其聪明彊敏。有记性者。或一览辄诵。至终身不忘。斯则可谓奇矣。而自古昔以来。固不多得。此岂人人之所可彊而能者哉。是以古之君子。已有病乎此。而欲无至于忘失者。又有抄录之事焉。此祝穆之所以作事文者也。余平生好博观古书。而性不能善记。未过数纸而已不省其前。如此而欲该通天下之书。何以异于梦游数千里山川而觉来思之。茫然不知所适哉。于是效祝公之为。作册置傍。随所览而辄记之。但不分类不立目。杂然而录之。此稍异于事文。且事文则所记浩博。珠砾并收。而余则但取其悦于心利于行者。至于医方杂法。有切于人事者。亦或载之。是乃如我鲁钝善忘者之事。苟有聪敏彊记之性如张巡者何事于是哉。或曰。子方以家贫亲老。欲取科第求禄仕。而不专力于时文。切切然分精于閒杂不紧之工。以费光阴。窃为君苦之。余答曰。子之言诚然矣。然人苟有诚。则虽朝耕而夜读。尚能成其功。况此录之勤。未及于耕耨之苦。而亦不无有补于时文者乎。昔王元美修苏长公外集序曰。时时咀嚼。其不贤于山腴海错者。几希。若此录者。岂特外集而已哉。客笑而去。遂书之。以为杂录序。丁亥腊月二十六日夜。书。
士以书为业。天下之书。无不该通而后。可以称士之名。而书籍浩漫。不可以随编烂读。于是乎有记览之工焉。然其聪明彊敏。有记性者。或一览辄诵。至终身不忘。斯则可谓奇矣。而自古昔以来。固不多得。此岂人人之所可彊而能者哉。是以古之君子。已有病乎此。而欲无至于忘失者。又有抄录之事焉。此祝穆之所以作事文者也。余平生好博观古书。而性不能善记。未过数纸而已不省其前。如此而欲该通天下之书。何以异于梦游数千里山川而觉来思之。茫然不知所适哉。于是效祝公之为。作册置傍。随所览而辄记之。但不分类不立目。杂然而录之。此稍异于事文。且事文则所记浩博。珠砾并收。而余则但取其悦于心利于行者。至于医方杂法。有切于人事者。亦或载之。是乃如我鲁钝善忘者之事。苟有聪敏彊记之性如张巡者何事于是哉。或曰。子方以家贫亲老。欲取科第求禄仕。而不专力于时文。切切然分精于閒杂不紧之工。以费光阴。窃为君苦之。余答曰。子之言诚然矣。然人苟有诚。则虽朝耕而夜读。尚能成其功。况此录之勤。未及于耕耨之苦。而亦不无有补于时文者乎。昔王元美修苏长公外集序曰。时时咀嚼。其不贤于山腴海错者。几希。若此录者。岂特外集而已哉。客笑而去。遂书之。以为杂录序。丁亥腊月二十六日夜。书。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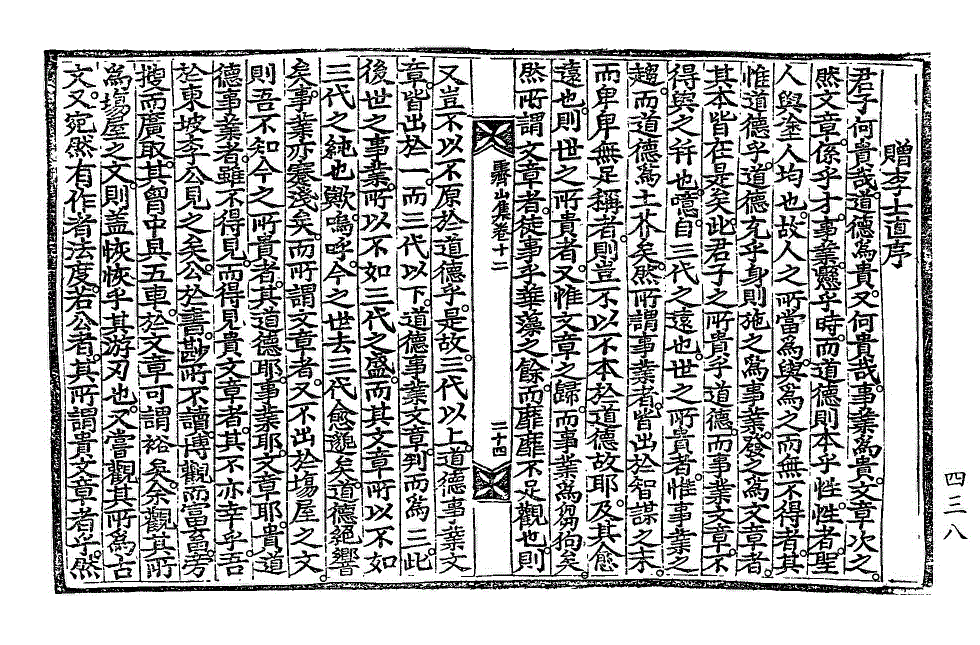 赠李士直序
赠李士直序君子何贵哉。道德为贵。又何贵哉。事业为贵。文章次之。然文章。系乎才。事业。悬乎时。而道德则本乎性。性者。圣人与涂人均也。故人之所当为。与为之而无不得者。其惟道德乎。道德充乎身则施之为事业。发之为文章者。其本皆在是矣。此君子之所贵乎道德。而事业文章。不得与之并也。噫。自三代之远也。世之所贵者。惟事业之趋。而道德为土芥矣。然所谓事业者。皆出于智谋之末。而卑卑无足称者。则岂不以不本于道德故耶。及其愈远也。则世之所贵者。又惟文章之归。而事业为刍狗矣。然所谓文章者。徒事乎华藻之馀。而靡靡不足观也。则又岂不以不原于道德乎。是故。三代以上。道德事业文章。皆出于一。而三代以下。道德事业文章。判而为三。此后世之事业。所以不如三代之盛。而其文章所以不如三代之纯也欤。呜呼。今之世去三代愈邈矣。道德绝响矣。事业亦蹇浅矣。而所谓文章者。又不出于场屋之文。则吾不知今之所贵者。其道德耶。事业耶。文章耶。贵道德事业者。虽不得见。而得见贵文章者。其不亦幸乎。吾于东坡李公见之矣。公于书。鲜所不读。博观而富畜。旁搜而广取。其胸中具五车。于文章可谓裕矣。余观其所为场屋之文。则盖恢恢乎其游刃也。又尝观其所为古文。又宛然有作者法度。若公者。其所谓贵文章者乎。然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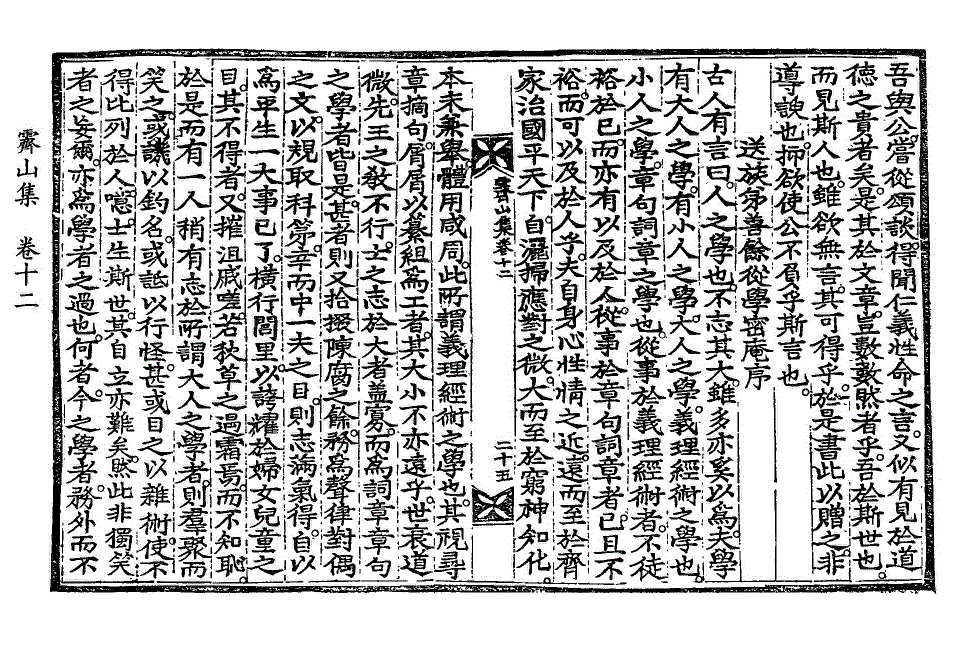 吾与公。尝从颂谈。得闻仁义性命之言。又似有见于道德之贵者矣。是其于文章。岂数数然者乎。吾于斯世也。而见斯人也。虽欲无言。其可得乎。于是书此以赠之。非导谀也。抑欲使公不负乎斯言也。
吾与公。尝从颂谈。得闻仁义性命之言。又似有见于道德之贵者矣。是其于文章。岂数数然者乎。吾于斯世也。而见斯人也。虽欲无言。其可得乎。于是书此以赠之。非导谀也。抑欲使公不负乎斯言也。送族弟善馀从学密庵序
古人有言曰。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亦奚以为。夫学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大人之学。义理经术之学也。小人之学。章句词章之学也。从事于义理经术者。不徒裕于己。而亦有以及于人。从事于章句词章者。己且不裕。而可以及于人乎。夫自身心性情之近。远而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洒扫应对之微。大而至于穷神知化。本末兼举。体用咸周。此所谓义理经术之学也。其视寻章摘句。屑屑以纂组为工者。其大小不亦远乎。世衰道微。先王之教不行。士之志于大者盖寡。而为词章章句之学者皆是。甚者则又拾掇陈腐之馀。务为声律对偶之文。以规取科第。幸而中一夫之目。则志满气得。自以为平生一大事已了。横行闾里。以誇耀于妇女儿童之目。其不得者。又摧沮戚嗟。若秋草之遇霜焉。而不知耻。于是而有一人稍有志于所谓大人之学者。则群聚而笑之。或讥以钓名。或诋以行怪。甚或目之以杂术。使不得比列于人。噫。士生斯世。其自立亦难矣。然此非独笑者之妄尔。亦为学者之过也。何者。今之学者。务外而不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L 页
 务内。求名而不求实。其号为自守者。必为崖异迂僻之行。而不趋于平实。号为通博者。或窃先儒已陈之说。以文其言。论天人性命之理。无不信口腾舌。而考其行。则反不如彼词章科目之人者多矣。是固无以异于昏夜穿窬之盗。而犹欲以学者自处。则彼之笑之者。亦奚足怪哉。余之再从弟庆锡。亦有志者也。去年冬。以亲命从梧台李丈学。读邹书及大学或问等书。今年冬。又以命赴函席。晨则告别。余扣其箧。即近思录数卷。将以是往质焉。余谓李丈。乃葛庵先生之子也。文章学问。最得其家传。则其于大人之学。必熟讲而有得焉。而近思录又周程张诸先生之格言至论。而紫阳朱夫子及东莱吕先生。相与编次者也。天命之微。人事之显。格致诚正之方。修齐治平之要。俱在于是。此即所谓大人之学也。士而无志则已。士而有志于大。则非是书何读。而非李丈谁从而讲之。今君之所从学及其所读。皆是也。吾复何言哉。吾之所欲言者。惟笃志而不懈。立脚而不挠。先以近思二字。为学问之要法。而无务外求名之失。始不为世俗之所变易。而终见信于世俗之人。以无负父师之望。而卒为大人焉。则幸矣。余科臼中人也。曩者。亦尝从葛庵先生。蒙教督之恩甚至。而志懦气弱。不能自奋。至于山颓之后。益以污下。无觊于少进。其终为小人之归。而得罪于师门也昭昭矣。今于君之行。不能无愧且羡
务内。求名而不求实。其号为自守者。必为崖异迂僻之行。而不趋于平实。号为通博者。或窃先儒已陈之说。以文其言。论天人性命之理。无不信口腾舌。而考其行。则反不如彼词章科目之人者多矣。是固无以异于昏夜穿窬之盗。而犹欲以学者自处。则彼之笑之者。亦奚足怪哉。余之再从弟庆锡。亦有志者也。去年冬。以亲命从梧台李丈学。读邹书及大学或问等书。今年冬。又以命赴函席。晨则告别。余扣其箧。即近思录数卷。将以是往质焉。余谓李丈。乃葛庵先生之子也。文章学问。最得其家传。则其于大人之学。必熟讲而有得焉。而近思录又周程张诸先生之格言至论。而紫阳朱夫子及东莱吕先生。相与编次者也。天命之微。人事之显。格致诚正之方。修齐治平之要。俱在于是。此即所谓大人之学也。士而无志则已。士而有志于大。则非是书何读。而非李丈谁从而讲之。今君之所从学及其所读。皆是也。吾复何言哉。吾之所欲言者。惟笃志而不懈。立脚而不挠。先以近思二字。为学问之要法。而无务外求名之失。始不为世俗之所变易。而终见信于世俗之人。以无负父师之望。而卒为大人焉。则幸矣。余科臼中人也。曩者。亦尝从葛庵先生。蒙教督之恩甚至。而志懦气弱。不能自奋。至于山颓之后。益以污下。无觊于少进。其终为小人之归。而得罪于师门也昭昭矣。今于君之行。不能无愧且羡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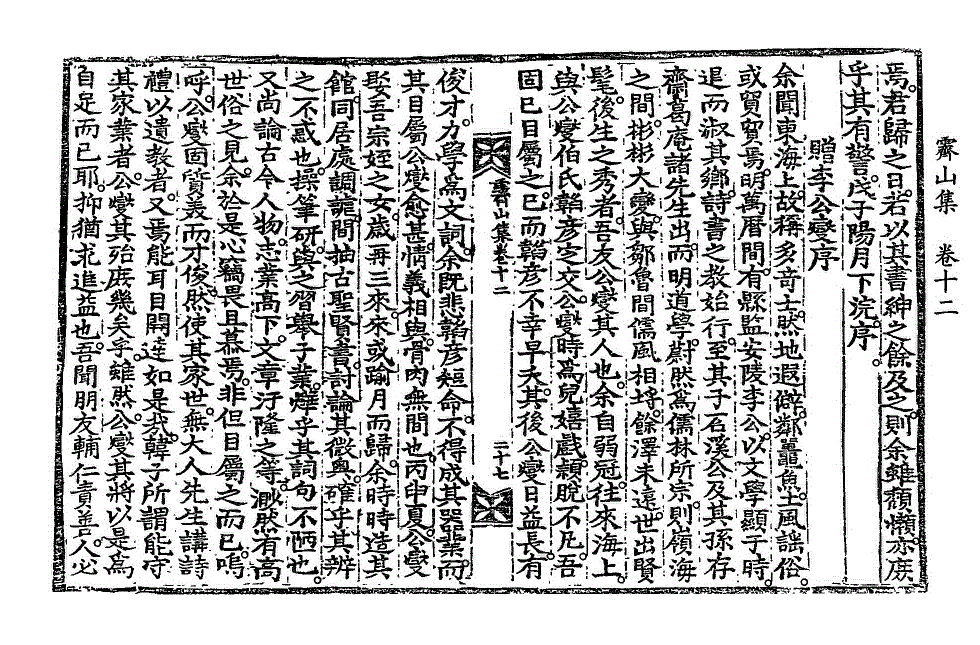 焉。君归之日。若以其书绅之馀及之。则余虽颓懒。亦庶乎其有警。戊子阳月下浣。序。
焉。君归之日。若以其书绅之馀及之。则余虽颓懒。亦庶乎其有警。戊子阳月下浣。序。赠李公燮序
余闻东海上。故称多奇士。然地遐僻。邻鼍鱼。土风谣俗。或贸贸焉。明万历间。有县监安陵李公。以文学显于时。退而淑其乡。诗书之教始行。至其子石溪公及其孙存斋,葛庵诸先生出。而明道学。蔚然为儒林所宗。则岭海之间。彬彬大变。与邹鲁间儒风相埒。馀泽未远。世出贤髦。后生之秀者。吾友公燮其人也。余自弱冠。往来海上。与公燮伯氏韬彦定交。公燮时为儿嬉戏。颖脱不凡。吾固已目属之。已而韬彦不幸早夭。其后公燮日益长。有俊才。力学为文词。余既悲韬彦短命。不得成其器业。而其目属公燮愈甚。情义相与。骨肉无间也。丙申夏。公燮娶吾宗侄之女。岁再三来。来或踰月而归。余时时造其馆。同居处调谑。间抽古圣贤书。讨论其微奥。确乎其辨之不惑也。操笔研。与之习举子业。烨乎其词句不陋也。又尚论古今人物。志业高下。文章污隆之等。渺然有高世俗之见。余于是心窃畏且慕焉。非但目属之而已。呜呼。公燮固质美而才俊。然使其家世。无大人先生讲诗礼以遗教者。又焉能耳目开达如是哉。韩子所谓能守其家业者。公燮其殆庶几矣乎。虽然公燮其将以是为自足而已耶。抑犹求进益也。吾闻朋友辅仁责善。人必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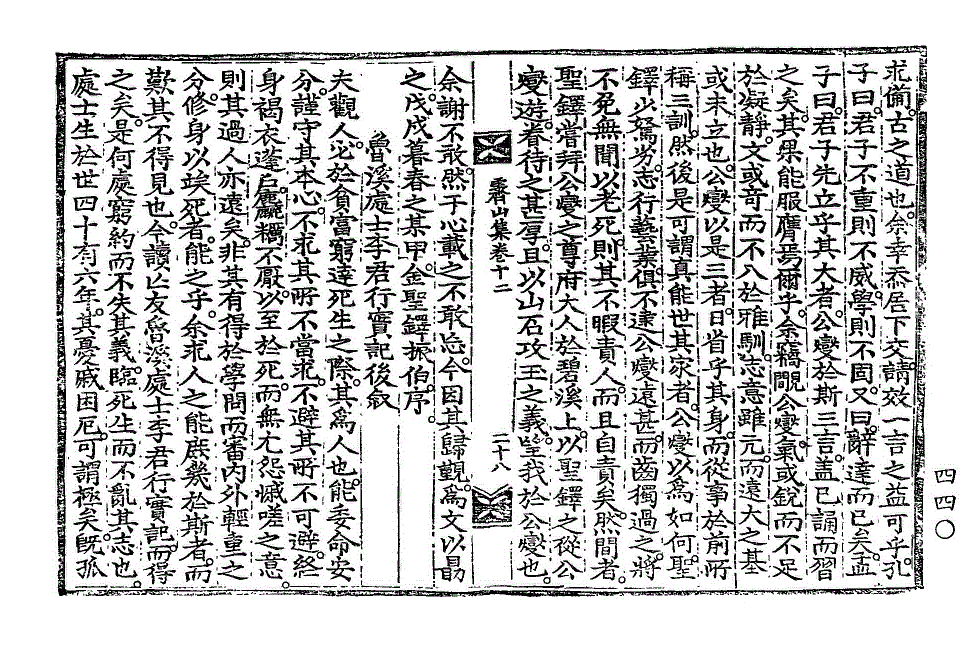 求备。古之道也。余幸忝居下交。请效一言之益可乎。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又曰。辞达而已矣。孟子曰。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公燮于斯三言。盖已诵而习之矣。其果能服膺焉尔乎。余窃覸公燮。气或锐而不足于凝静。文或奇而不入于雅驯。志意虽亢。而远大之基或未立也。公燮以是三者。日省乎其身。而从事于前所称三训。然后是可谓真能世其家者。公燮以为如何。圣铎少驽劣。志行艺业。俱不逮公燮远甚。而齿独过之。将不免无闻以老死。则其不暇责人。而且自责矣。然间者。圣铎尝拜公燮之尊府大人于碧溪上。以圣铎之从公燮游。眷待之甚厚。且以山石攻玉之义。望我于公燮也。余谢不敢。然于心载之不敢忘。今因其归觐。为文以勖之。戊戌暮春之某甲。金圣铎振伯。序。
求备。古之道也。余幸忝居下交。请效一言之益可乎。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又曰。辞达而已矣。孟子曰。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公燮于斯三言。盖已诵而习之矣。其果能服膺焉尔乎。余窃覸公燮。气或锐而不足于凝静。文或奇而不入于雅驯。志意虽亢。而远大之基或未立也。公燮以是三者。日省乎其身。而从事于前所称三训。然后是可谓真能世其家者。公燮以为如何。圣铎少驽劣。志行艺业。俱不逮公燮远甚。而齿独过之。将不免无闻以老死。则其不暇责人。而且自责矣。然间者。圣铎尝拜公燮之尊府大人于碧溪上。以圣铎之从公燮游。眷待之甚厚。且以山石攻玉之义。望我于公燮也。余谢不敢。然于心载之不敢忘。今因其归觐。为文以勖之。戊戌暮春之某甲。金圣铎振伯。序。鲁溪处士李君行实记后叙
夫观人。必于贫富穷达死生之际。其为人也。能委命安分。谨守其本心。不求其所不当求。不避其所不可避。终身褐衣蓬户。粗粝不厌。以至于死。而无尤怨戚嗟之意。则其过人亦远矣。非其有得于学问而审内外轻重之分。修身以俟死者。能之乎。余求人之能庶几于斯者。而叹其不得见也。今读亡友鲁溪处士李君行实记。而得之矣。是何处穷约而不失其义。临死生而不乱其志也。处士生于世四十有六年。其忧戚困厄。可谓极矣。既孤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H 页
 露丧兄弟。踽踽无所归。或在锦水。或返南谷故居。或就食大江之表。流离转徙。盖无四三年奠厥居者。而所止又率乏资计。往往空匮寒冻。人不堪其苦。而处士处之晏如。未尝以口腹故。有所俯仰于人。视世之名利芬华。泊然无所动于中。而惟以读书修行。不坠家世遗教。为务。善乎。其自道其志之语曰。贫贱非不厌。吾不知其戚戚而去之。富贵非不欲。吾不知其汲汲而求之。与其营营而生。区区而荣。不若颠沟壑死岩穴之为愈。推此志也。即千驷万钟。不以易其介。箪瓢陋巷。不以改其乐者。可庶几焉。惟其所养者如是。故其没也。所以遗命教戒于其子。及正身敛手足。以全归其父母遗体者。可谓得君子之正终。呜呼。岂不贤哉。是非学问之力。何以及此。处士生于文献之家。逮事其王父葛庵先生。聪明醇雅。耳目濡染。已能服习诗礼之训。及先生没。又从其叔父密庵先生。讲质问难。究极底蕴。而出则游于玉山申克斋明仲。上下磨砻。旁通曲畅。其学自太极阴阳四七理气等说。盖已不畔于家学之旨。而至于礼乐象数图书之原。亦莫不精通妙解。无所底滞。密翁尝称之曰。是真学者也。门户之托在此。又尝听其所讲阴阳之说。而喜之曰。吾于汝。所资益颇多云。而克斋亦每以彊辅许之。则其学之所至。槩可知矣。且吾于处士论学之言。有所警矣。曰学问之道。在于穷理致知反躬践实。而要其归
露丧兄弟。踽踽无所归。或在锦水。或返南谷故居。或就食大江之表。流离转徙。盖无四三年奠厥居者。而所止又率乏资计。往往空匮寒冻。人不堪其苦。而处士处之晏如。未尝以口腹故。有所俯仰于人。视世之名利芬华。泊然无所动于中。而惟以读书修行。不坠家世遗教。为务。善乎。其自道其志之语曰。贫贱非不厌。吾不知其戚戚而去之。富贵非不欲。吾不知其汲汲而求之。与其营营而生。区区而荣。不若颠沟壑死岩穴之为愈。推此志也。即千驷万钟。不以易其介。箪瓢陋巷。不以改其乐者。可庶几焉。惟其所养者如是。故其没也。所以遗命教戒于其子。及正身敛手足。以全归其父母遗体者。可谓得君子之正终。呜呼。岂不贤哉。是非学问之力。何以及此。处士生于文献之家。逮事其王父葛庵先生。聪明醇雅。耳目濡染。已能服习诗礼之训。及先生没。又从其叔父密庵先生。讲质问难。究极底蕴。而出则游于玉山申克斋明仲。上下磨砻。旁通曲畅。其学自太极阴阳四七理气等说。盖已不畔于家学之旨。而至于礼乐象数图书之原。亦莫不精通妙解。无所底滞。密翁尝称之曰。是真学者也。门户之托在此。又尝听其所讲阴阳之说。而喜之曰。吾于汝。所资益颇多云。而克斋亦每以彊辅许之。则其学之所至。槩可知矣。且吾于处士论学之言。有所警矣。曰学问之道。在于穷理致知反躬践实。而要其归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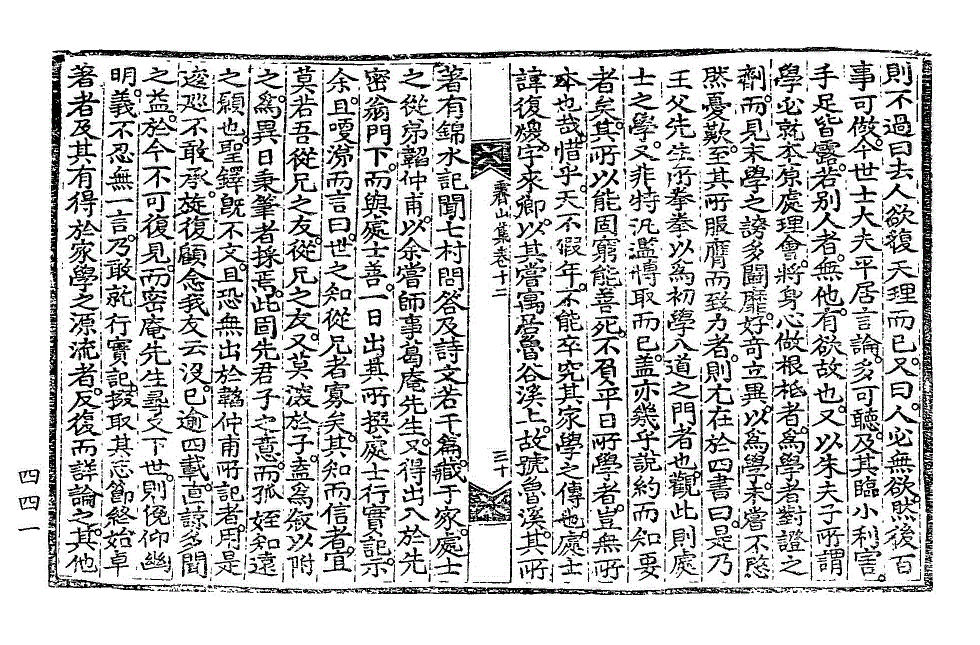 则不过曰去人欲复天理而已。又曰。人必无欲。然后百事可做。今世士大夫平居言论。多可听。及其临小利害。手足皆露。若别人者。无他。有欲故也。又以朱夫子所谓学必就本原处理会。将身心做根柢者。为学者对證之剂。而见末学之誇多斗靡。好奇立异。以为学。未尝不悯然忧叹。至其所服膺而致力者。则尤在于四书曰。是乃王父先生所拳拳以为初学入道之门者也。观此则处士之学。又非特汎滥博取而已。盖亦几乎说约而知要者矣。其所以能固穷能善死。不负平日所学者。岂无所本也哉。惜乎。天不假年。不能卒究其家学之传也。处士讳复焕。字来卿。以其尝寓居鲁谷溪上。故号鲁溪。其所著有锦水记闻,七村问答及诗文若干篇。藏于家。处士之从弟韬仲甫。以余尝师事葛庵先生。又得出入于先密翁门下。而与处士善。一日出其所撰处士行实记。示余。且哽涕而言曰。世之知从兄者寡矣。其知而信者。宜莫若吾从兄之友。从兄之友。又莫深于子。盍为叙以附之。为异日秉笔者采焉。此固先君子之意。而孤侄知远之愿也。圣铎既不文。且恐无出于韬仲甫所记者。用是逡巡不敢承。旋复顾念我友云没。已逾四载。直谅多闻之益。于今不可复见。而密庵先生寻又下世。则俛仰幽明。义不忍无一言。乃敢就行实记。掇取其志节终始卓著者及其有得于家学之源流者。反复而详论之。其他
则不过曰去人欲复天理而已。又曰。人必无欲。然后百事可做。今世士大夫平居言论。多可听。及其临小利害。手足皆露。若别人者。无他。有欲故也。又以朱夫子所谓学必就本原处理会。将身心做根柢者。为学者对證之剂。而见末学之誇多斗靡。好奇立异。以为学。未尝不悯然忧叹。至其所服膺而致力者。则尤在于四书曰。是乃王父先生所拳拳以为初学入道之门者也。观此则处士之学。又非特汎滥博取而已。盖亦几乎说约而知要者矣。其所以能固穷能善死。不负平日所学者。岂无所本也哉。惜乎。天不假年。不能卒究其家学之传也。处士讳复焕。字来卿。以其尝寓居鲁谷溪上。故号鲁溪。其所著有锦水记闻,七村问答及诗文若干篇。藏于家。处士之从弟韬仲甫。以余尝师事葛庵先生。又得出入于先密翁门下。而与处士善。一日出其所撰处士行实记。示余。且哽涕而言曰。世之知从兄者寡矣。其知而信者。宜莫若吾从兄之友。从兄之友。又莫深于子。盍为叙以附之。为异日秉笔者采焉。此固先君子之意。而孤侄知远之愿也。圣铎既不文。且恐无出于韬仲甫所记者。用是逡巡不敢承。旋复顾念我友云没。已逾四载。直谅多闻之益。于今不可复见。而密庵先生寻又下世。则俛仰幽明。义不忍无一言。乃敢就行实记。掇取其志节终始卓著者及其有得于家学之源流者。反复而详论之。其他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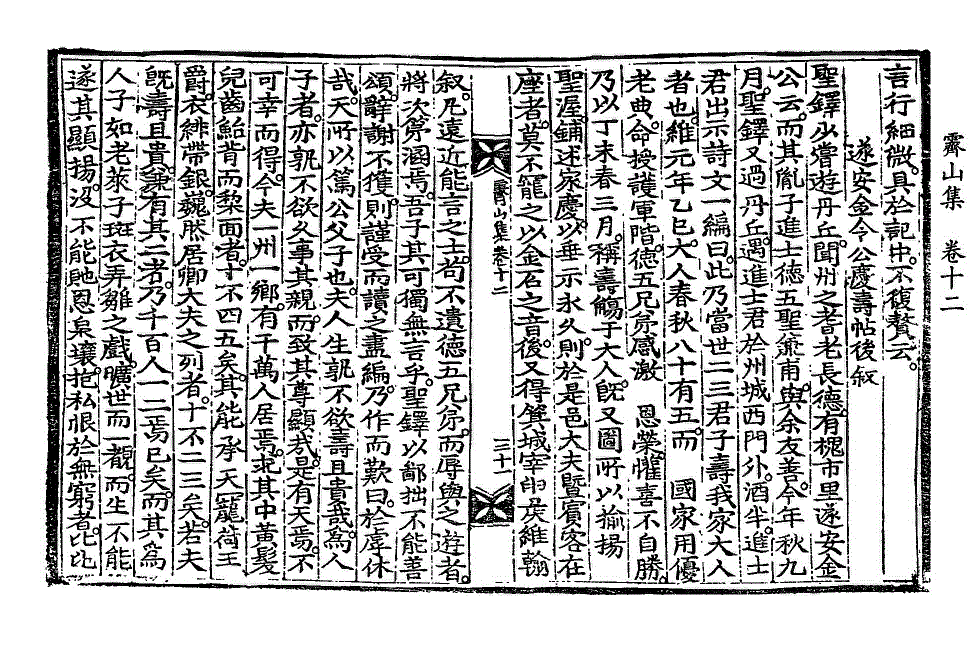 言行细微。具于记中。不复赘云。
言行细微。具于记中。不复赘云。遂安金令公庆寿帖后叙
圣铎少尝游丹丘。闻州之耆老长德。有槐市里遂安金公云。而其胤子进士德五圣兼甫。与余友善。今年秋九月。圣铎又过丹丘。遇进士君于州城西门外。酒半。进士君出示诗文一编曰。此乃当世二三君子寿我家大人者也。维元年乙巳。大人春秋八十有五。而 国家用优老典。命授护军阶。德五兄弟感激 恩荣。欢喜不自胜。乃以丁未春三月。称寿觞于大人。既又图所以揄扬 圣渥。铺述家庆。以垂示永久。则于是邑大夫暨宾客在座者。莫不宠之以金石之音。后又得箕城宰申侯维翰叙。凡远近能言之士。苟不遗德五兄弟。而辱与之游者。将次第溷焉。吾子其可独无言乎。圣铎以鄙拙不能善颂。辞谢不获。则谨受而读之尽编。乃作而叹曰。于虖休哉。天所以笃公父子也。夫人生孰不欲寿且贵哉。为人子者。亦孰不欲久事其亲。而致其尊显哉。是有天焉。不可幸而得。今夫一州一乡。有千万人居焉。求其中黄发儿齿鲐背而梨面者。十不四五矣。其能承天宠荷王爵。衣绯带银。巍然居卿大夫之列者。十不二三矣。若夫既寿且贵。兼有其二者。乃千百人一二焉已矣。而其为人子如老莱子斑衣弄雏之戏。旷世而一睹。而生不能遂其显扬。没不能貤恩泉壤。抱私恨于无穷者。比比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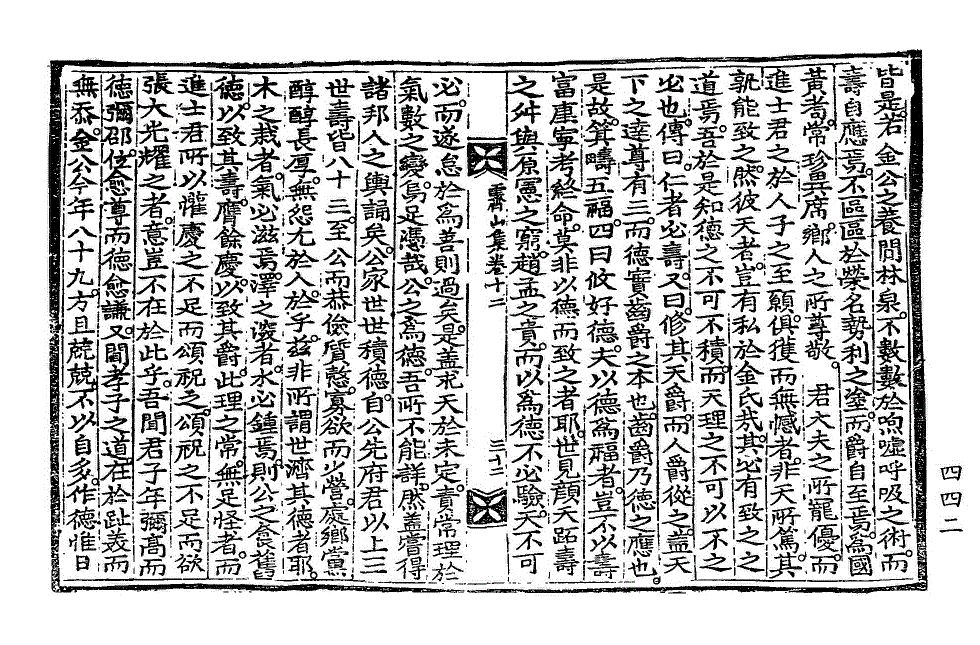 皆是。若金公之养閒林泉。不数数于喣嘘呼吸之术。而寿自应焉。不区区于荣名势利之涂。而爵自至焉。为国黄耇。常珍异席。乡人之所尊敬。 君大夫之所宠优。而进士君之于人子之至愿。俱获而无憾者。非天所笃。其孰能致之。然彼天者。岂有私于金氏哉。其必有致之之道焉。吾于是知德之不可不积。而天理之不可以不之必也。传曰。仁者必寿。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天下之达尊有三。而德实齿爵之本也。齿爵乃德之应也。是故。箕畴五福。四曰攸好德。夫以德为福者。岂不以寿富康宁考终命。莫非以德而致之者耶。世见颜夭蹠寿之舛与原宪之穷。赵孟之贵。而以为德不必验。天不可必。而遂怠于为善则过矣。是盖求天于未定。责常理于气数之变。乌足凭哉。公之为德。吾所不能详。然盖尝得诸邦人之舆诵矣。公家世世积德。自公先府君以上三世寿皆八十三。至公而恭俭质悫。寡欲而少营。处乡党醇醇长厚。无怨尤于人。于乎。玆非所谓世济其德者耶。木之栽者。气必滋焉。泽之深者。水必钟焉。则公之食旧德。以致其寿。膺馀庆。以致其爵。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而进士君所以欢庆之不足而颂祝之。颂祝之不足而欲张大光耀之者。意岂不在于此乎。吾闻君子年弥高而德弥卲。位愈尊而德愈谦。又闻孝子之道。在于趾美而无忝。金公今年八十九。方且兢兢。不以自多。作德惟日
皆是。若金公之养閒林泉。不数数于喣嘘呼吸之术。而寿自应焉。不区区于荣名势利之涂。而爵自至焉。为国黄耇。常珍异席。乡人之所尊敬。 君大夫之所宠优。而进士君之于人子之至愿。俱获而无憾者。非天所笃。其孰能致之。然彼天者。岂有私于金氏哉。其必有致之之道焉。吾于是知德之不可不积。而天理之不可以不之必也。传曰。仁者必寿。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天下之达尊有三。而德实齿爵之本也。齿爵乃德之应也。是故。箕畴五福。四曰攸好德。夫以德为福者。岂不以寿富康宁考终命。莫非以德而致之者耶。世见颜夭蹠寿之舛与原宪之穷。赵孟之贵。而以为德不必验。天不可必。而遂怠于为善则过矣。是盖求天于未定。责常理于气数之变。乌足凭哉。公之为德。吾所不能详。然盖尝得诸邦人之舆诵矣。公家世世积德。自公先府君以上三世寿皆八十三。至公而恭俭质悫。寡欲而少营。处乡党醇醇长厚。无怨尤于人。于乎。玆非所谓世济其德者耶。木之栽者。气必滋焉。泽之深者。水必钟焉。则公之食旧德。以致其寿。膺馀庆。以致其爵。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而进士君所以欢庆之不足而颂祝之。颂祝之不足而欲张大光耀之者。意岂不在于此乎。吾闻君子年弥高而德弥卲。位愈尊而德愈谦。又闻孝子之道。在于趾美而无忝。金公今年八十九。方且兢兢。不以自多。作德惟日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H 页
 不足。而进士君承义方敦孝弟。于家世钟德之休。不替而又有光焉。则天之所以笃金氏之福。其永永无彊哉。圣铎不敏。未及一拜公床下。然丹丘。余所游也。异日倘获升公之堂。酌大斗赋南山。祝万万寿。归以詑于人曰。吾见安期,羡门子于东海上。未晚也。系之以诗。诗三章章四句。
不足。而进士君承义方敦孝弟。于家世钟德之休。不替而又有光焉。则天之所以笃金氏之福。其永永无彊哉。圣铎不敏。未及一拜公床下。然丹丘。余所游也。异日倘获升公之堂。酌大斗赋南山。祝万万寿。归以詑于人曰。吾见安期,羡门子于东海上。未晚也。系之以诗。诗三章章四句。海有洲。山有冈。乐只君子。万寿无彊。(兴也。)山有冈。海有洲。乐只君子。福禄来求。(兴也。)瞻彼中原。庶民采菽。凡百君子。曷不好德。(兴也。)
知非录序
知非录。何为而名也。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今年适四十九。故取以名之也。夫伯玉。卫之贤大夫。而孔子所称为君子者也。以其见于论语及他传记者。其平居。欲寡其过而未能。不以闇昧而惰行废礼。则是其言动事为之间。岂有显然尤悔哉。其所谓非。不过邵子所谓心过。程子所谓才差失之比耳。然其省身克己。日新又新。至于六十而犹有化之之功。则况乎后之学者。其贤远不及伯玉者哉。其可以年齿之衰迈。自废而不为之省念哉。余自八岁入学。至于今四十有馀年。而发于思虑。形于言动。悖于德而违于礼者。盖什常八九矣。惟其昏愚钝滞。不自觉知。昨日之非。今日复行。前岁之非。后岁复蹈。荏苒积累。不但如磨驴之踏旧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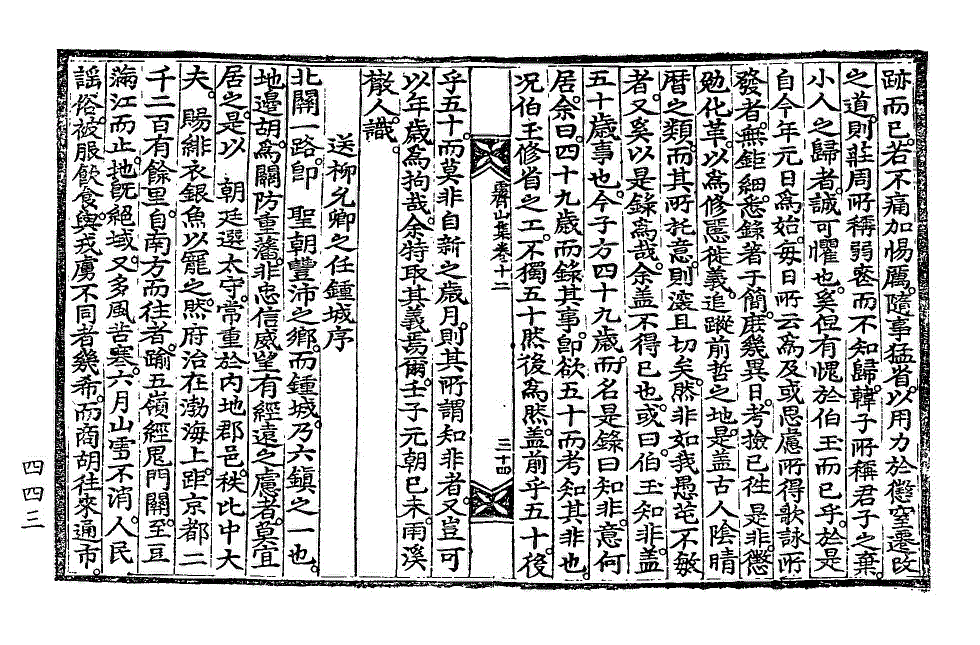 迹而已。若不痛加惕厉。随事猛省。以用力于惩窒迁改之道。则庄周所称弱丧而不知归。韩子所称君子之弃。小人之归者。诚可惧也。奚但有愧于伯玉而已乎。于是自今年元日为始。每日所云为及或思虑所得歌咏所发者。无钜细。悉录著于简。庶几异日。考捡已往是非。惩勉化革。以为修慝徙义。追踪前哲之地。是盖古人阴晴历之类。而其所托意。则深且切矣。然非如我愚芚不敏者。又奚以是录为哉。余盖不得已也。或曰。伯玉知非。盖五十岁事也。今子方四十九岁。而名是录曰知非。意何居。余曰。四十九岁而录其事。即欲五十而考知其非也。况伯玉修省之工。不独五十然后为然。盖前乎五十。后乎五十。而莫非自新之岁月。则其所谓知非者。又岂可以年岁为拘哉。余特取其义焉尔。壬子元朝己未。雨溪散人。识。
迹而已。若不痛加惕厉。随事猛省。以用力于惩窒迁改之道。则庄周所称弱丧而不知归。韩子所称君子之弃。小人之归者。诚可惧也。奚但有愧于伯玉而已乎。于是自今年元日为始。每日所云为及或思虑所得歌咏所发者。无钜细。悉录著于简。庶几异日。考捡已往是非。惩勉化革。以为修慝徙义。追踪前哲之地。是盖古人阴晴历之类。而其所托意。则深且切矣。然非如我愚芚不敏者。又奚以是录为哉。余盖不得已也。或曰。伯玉知非。盖五十岁事也。今子方四十九岁。而名是录曰知非。意何居。余曰。四十九岁而录其事。即欲五十而考知其非也。况伯玉修省之工。不独五十然后为然。盖前乎五十。后乎五十。而莫非自新之岁月。则其所谓知非者。又岂可以年岁为拘哉。余特取其义焉尔。壬子元朝己未。雨溪散人。识。送柳允卿之任钟城序
北关一路。即 圣朝丰沛之乡。而钟城。乃六镇之一也。地边胡。为关防重藩。非忠信威望有经远之虑者。莫宜居之。是以 朝廷选太守。常重于内地郡邑。秩比中大夫。 赐绯衣银鱼以宠之。然府治在渤海上。距京都二千二百有馀里。自南方而往者。踰五岭经鬼门关。至豆满江而止。地既绝域。又多风苦寒。六月山雪不消。人民谣俗。被服饮食。与戎虏不同者几希。而商胡往来通市。
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H 页
 一或失御。辄凭凌慢肆。若豨突然。故凡仕稍有倚藉。率避不往。其往者。皆名士之不偶时。而无先后扳联之势于朝者也。柳侯允卿甫。释褐屡岁。不离即署。弃官归田园有年。今年春。以司宪府掌令。起家赴 召。中道而递。未几又拜宗簿正。将趋肃。而有钟城之 命。其行也。人或贺其升秩。或慰其远宦。侯既不以人之贺为喜。又不以人之慰为戚。出门别妻子。无惘惘可怜之色。观其意。毅然若将徇国忘家。不择险夷为去就者。而其忠忱远虑。隐然有古人风。庶几可以慎固封守。镇服民夷。不负 圣上所以委任保障之意。余于是叹而贤之曰。为仕者。无远近无内外无难易。唯随所处而尽其职。不以荣辱利害累其中。然后可以为人臣事君之道。彼舍远而就近。规内而辞外。避难而处易者。利而已私而已。非忠于君国者所忍为。是乃柳侯之羞也。且余有所感矣。大丈夫穷则已。既达而立乎人之本朝。不得处人主帷幄中。朝夕论思。陈尧舜之道。则无宁分铜虎竹使符。专制一大镇。或兴儒教。化其朴鄙之俗。如文翁之在蜀。或讲武略。使敌人破胆。如小范之在陕西。岂非幼学壮行者之志愿事功哉。吾闻 国初。有金公宗瑞。开拓六镇。功烈伟然。无愧丽之尹瓘。而近世有葛庵李先生。谪居是州。讲道学。州之士。往往奋兴。若朱楗其杰然者也。侯若有志文武之事。则请礼朱生。若韩文公之于赵德。以帅
一或失御。辄凭凌慢肆。若豨突然。故凡仕稍有倚藉。率避不往。其往者。皆名士之不偶时。而无先后扳联之势于朝者也。柳侯允卿甫。释褐屡岁。不离即署。弃官归田园有年。今年春。以司宪府掌令。起家赴 召。中道而递。未几又拜宗簿正。将趋肃。而有钟城之 命。其行也。人或贺其升秩。或慰其远宦。侯既不以人之贺为喜。又不以人之慰为戚。出门别妻子。无惘惘可怜之色。观其意。毅然若将徇国忘家。不择险夷为去就者。而其忠忱远虑。隐然有古人风。庶几可以慎固封守。镇服民夷。不负 圣上所以委任保障之意。余于是叹而贤之曰。为仕者。无远近无内外无难易。唯随所处而尽其职。不以荣辱利害累其中。然后可以为人臣事君之道。彼舍远而就近。规内而辞外。避难而处易者。利而已私而已。非忠于君国者所忍为。是乃柳侯之羞也。且余有所感矣。大丈夫穷则已。既达而立乎人之本朝。不得处人主帷幄中。朝夕论思。陈尧舜之道。则无宁分铜虎竹使符。专制一大镇。或兴儒教。化其朴鄙之俗。如文翁之在蜀。或讲武略。使敌人破胆。如小范之在陕西。岂非幼学壮行者之志愿事功哉。吾闻 国初。有金公宗瑞。开拓六镇。功烈伟然。无愧丽之尹瓘。而近世有葛庵李先生。谪居是州。讲道学。州之士。往往奋兴。若朱楗其杰然者也。侯若有志文武之事。则请礼朱生。若韩文公之于赵德。以帅霁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L 页
 州人。而询故老按图记。求金公施设之方。则几矣。柳侯其勉乎哉。柳侯于余。有兄弟之分。临行要一言以赠。故为之序。勉以大义。不敢效儿女子作惜别语者。恐为柳侯所笑也。继以唐律一篇。(诗见诗卷。)
州人。而询故老按图记。求金公施设之方。则几矣。柳侯其勉乎哉。柳侯于余。有兄弟之分。临行要一言以赠。故为之序。勉以大义。不敢效儿女子作惜别语者。恐为柳侯所笑也。继以唐律一篇。(诗见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