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凤岩集卷之六 第 x 页
凤岩集卷之六
书
书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6H 页
 答玉所权调元(燮○问解疑目○戊午)
答玉所权调元(燮○问解疑目○戊午)疑礼问解祠堂条第七板后寝。答说通五架一大梁云云。若加一大梁。则明是只作二间。而乃以只立两柱明矣。为答可疑。且神主藏于后寝房室中。而祭时出安前堂。祔位则设于东西序耶。东西厢。用于何时耶。
按五架屋之制。一大梁之两头。各受一横栋。是为前后二架。自前后架中分中脊之南北。各立短柱二。以擎前后横栋。是为次二架。并屋极所加中脊之栋为五架。故曰通五架一大梁而只立两柱云耳。非谓通一屋而只加一大梁也。如此则亦不成二间矣。东西厢。即东西序之外也。盖序在左右房之前。厢在左右夹室之前。朱先生曰。祔食之位。古人祭于东西厢。又曰。今人家无东西厢。某家只设位于堂之两边云。其为祭时设祔之处者可知。而无厢则似当设于序耳。
庶人祭及高祖。答说云云。大夫士庶人。虽三庙一庙及祭寝之有异。亦皆祭及高祖。则古何有庶人只祭考妣之文耶。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6L 页
 庶人无庙。只祭考妣于寝室。而大祫则及其高祖者礼也。所谓祭及高祖。非常祭之谓也。通典曰。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以新物荐。庶人既无庙。则荐新等事。固不及于高祖者可知。且庶人生不异宫。故死不异庙。而只祭于寝。此祭及高祖及只祭考妣之文。所以不同也。
庶人无庙。只祭考妣于寝室。而大祫则及其高祖者礼也。所谓祭及高祖。非常祭之谓也。通典曰。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以新物荐。庶人既无庙。则荐新等事。固不及于高祖者可知。且庶人生不异宫。故死不异庙。而只祭于寝。此祭及高祖及只祭考妣之文。所以不同也。家礼图第三板韬制。答说以通趺方为然。未知有何所据耶。既曰与主身齐。则趺方自是主身下一物。何可通称主身耶。此则断不然。而第以式如斗帐之斗字看之。如非并韬趺方者。则其制狭而长。不能如斗之方平矣。亦可疑也。
所谓长与主身齐者。似是通指主身一尺二寸而言。如或除趺方一寸二分而言。则恐当别有措语也。沙溪先生亦曰。合缝居后之中。稍留其末者。欲令并韬其趺也。今人或有只距趺面而不并韬者。恐非此当为定论。来谕所谓趺方自是主身下一物者恐误。主身既非趺方上所立者。则趺方安得为主身下一物乎。窃意韬长当与主身同。四广亦当如趺方而稍宽然后。乃合于古式。而私家曾用只距趺面之制。欲改而未能矣。今承所示如此。无乃贵宗亦用俗制耶。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7H 页
 宗法条第十板兄亡弟及后。兄妻立后。答说云云。虽无断语。其意则可知其以立后为然矣。但念次子既服三年丧。则次子便为嫡子。何可续续换易耶。抑前之服丧承重。已坏礼防。今乃以子继兄。改正宗统。果合礼意耶。
宗法条第十板兄亡弟及后。兄妻立后。答说云云。虽无断语。其意则可知其以立后为然矣。但念次子既服三年丧。则次子便为嫡子。何可续续换易耶。抑前之服丧承重。已坏礼防。今乃以子继兄。改正宗统。果合礼意耶。兄妻立后。归宗无疑。次子承统。初既失之。宁容再误。伊川家事。朱先生亦以为疑。而世或有以此起讼者。可戒。
第十五板班祔分排问目。家礼班祔于祖母之傍云云。答陈某妻丧条别庙云云。果相不同。而答说终无卞析之语。只以初非班祔之谓也为言。何耶。且问目中所谓祭时。右丈夫左妇女。或东西相向。尊者居右。而在庙则各从昭穆设者。果何义耶。
答语既以前数说为定论。此非卞析之语耶。妻先亡弟亡。各以一室云云者。非以班祔而言之。故曰初非班祔之谓也。即别室藏主之义云尔。在庙各从昭穆。祭时东西相向。礼不得不然。孙必祔祖。则不得不各从昭穆。祭不合嫂叔并坐。则不得不东西相向故耳。
第十六板侄之父立祠堂。答说下方宋龟峰说祖尚存云云。祖若尚存。则当以从子族子为称。何可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7L 页
 举孙为主而乃称侄之父耶。
举孙为主而乃称侄之父耶。龟峰所谓祖尚存者。指亡侄之祖而言也。无乃以宗子之祖看之耶。当初祔于宗家者。乃其从侄或再从侄。而今则其祖已死。其父自立祠堂。故曰侄之父。文字必如是而后。分明易见也。
别室藏主条第十七板。祭三代家别室祭高祖云云。既于第七板。虽庶人必祭及高祖条。以遵行此礼不为无据为答。则今于此。亦当劝使祭及高祖。乃独随问而随答者。抑何意耶。
庶人之祭及高祖。只以大祫而言也。与国制祭三代之祭不同。恐不可以一例看。
第二十二板襕衫。答说下方。以天中记之下加襕。朱子君臣服议之上领有襕。上衣下襕。大明集礼之下施横襕等说看之。则襕是衣中之一物。以唐志之着襕。邵尧夫之饭必襕等说看之。则襕是衣名。未知将何所适从。朱子君臣服议。既言上领有襕。又言上衣下襕。上下之说。自相径庭。亦似可疑。又长孙无忌议。则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庶人。皆得以服襕。而只有绯紫绿白之差异。而洪武年间。乃以玉色襕衫。定为生员服制。然则惟生员得以服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8H 页
 之。上之公卿大夫士。下之庶人。皆未得服。而又无绯紫绿白之差耶。所谓绯紫绿白云者。以绯紫绿白为衣。而纯则俱用黑绢耶。
之。上之公卿大夫士。下之庶人。皆未得服。而又无绯紫绿白之差耶。所谓绯紫绿白云者。以绯紫绿白为衣。而纯则俱用黑绢耶。襕是衣名。然衣以襕为名者。以其有襕也。洪武以前则公卿以下皆服之。以后则大夫以上。似不必服。士以下服。亦何妨。衫则勿论何色。缘则当用青黑二色。然黑色尤好。盖襕衫始制时。以布深衣着襕及裾云。则其缘似当与深衣同。古者深衣亦有青纯者耶。
第二十三板帽子。答说下方所云小帽者。其制何如。家礼辑览图所载之制。如今毛帽而有两缨。岂以纱罗段三物。造为此制耶。丘氏只云或纱或罗或段为之。而无或毛之语。未知毛帽之制则出于大明后耶。
小帽。五代蜀王衍晚年。俗竞为小帽尖。仅覆其顶云。如今所谓唐㔶头。然此则恐不合为祭时之首饰。毛帽别无可考处。而按丛书席帽。本羌人首服。以羊毛为之。秦汉竞服之。而妇人戴者。肆缘垂下以自蔽云。所谓毛帽。恐指此也。通典又曰。古者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纚为帽。此在辑览中。考之则可悉矣。盖俱非我国常制。似当以笠子或纱帽等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8L 页
 冠行之耶。
冠行之耶。假髻特髻。答说下方二仪实录。女子必有继于人云者。以女子适人有生子。继其世之道而言耶。周礼副编次注所谓步摇。其制何如。服之以桑之桑字。岂蚕桑之桑字耶。王后之从王祭。以桑以见王。以副编次为等者。岂其有轻重之差耶。
继非生子继世之义。如诗所谓缵女维莘。礼所谓先妣之嗣之意。燧人始编发为髻。至尧舜时。复加钗笄为首饰。文王于髻上。加翠翘花。又为凤髻云髻。加之以步摇。以其步步而摇故名。即诗所谓副笄六珈也。图见辑览开元中妇见舅姑时。有云戴步摇插翠钗。其制笄之两头。有六珈垂下如缀旒然。桑字分明是王后桑于公桑之桑。副编次之轻重未详。然周礼六服。第一袆衣。袆用副笄。故曰副袆。当为王后之首服。编者假髻也。妇女通用之。次亦如之。似有轻重之别。且以此注以祭以桑以王之文见之。其有等级者。可知矣。
俗节条第二十四板生忌之说。生指死者始初生世之日。以是日馈享者。甚无谓也。如忌者是丧馀之日。以追远之诚。设奠享死。虽非正祭。岂可大害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9H 页
 于理哉。退,沙两先生。亦皆行之自如。而于答人则以非礼之礼笑之。何也。岂所谓生忌者。以死者之生辰为生忌而非并指忌日耶。
于理哉。退,沙两先生。亦皆行之自如。而于答人则以非礼之礼笑之。何也。岂所谓生忌者。以死者之生辰为生忌而非并指忌日耶。生日。非但非古礼也。忌日亦然。故张子曰。古人于忌日。无荐献之礼。特致哀示变而已。语类亦曰。古无忌祭。近日诸先生方考及此。窃意三代以上则忌亦不祭。然祭仪有云忌者丧之馀。是日若不设祭。则何以出于祭仪中也。况程,朱两先生家。亦已行之。退,沙二先生。必无斥以非礼之理。所谓生忌。恐专指生辰而言也。然称之以忌。亦甚无谓。
第二十五板孝玄字义。答说下方郊特牲注。士之祭称孝子云云。祭主于孝。则人君士庶皆同。而独于士称孝字者。岂是礼自士始之故耶。其下两条玄字云云。既以斥犯圣祖讳改玄称元。则告事条时祭条。同是家礼中篇目。而或讳玄而改称元孙。或不讳而直称玄孙何耶。
祭之称孝。自士礼始。来教然矣。宋史。虽有讳玄之语。而事涉不经。私家文字。何必尽讳。考朱先生书。如慎字扩字。经传中。皆改用谨广。而玄字则直书而不讳。如易之玄黄。语之玄冠之类是也。所制诗中玄天玄
凤岩集卷之六 第 299L 页
 圣玄妙之类甚多。何独于礼经而讳之也。实未可知也。况元字近僭。先生初字。既以仲字改之。而玄孙之改以元孙。尤似未安。可疑。然丘说亦必有所据。姑阙之可也。告事条元字。岂丘氏悉改以从玄。有未能尽改者而然欤。
圣玄妙之类甚多。何独于礼经而讳之也。实未可知也。况元字近僭。先生初字。既以仲字改之。而玄孙之改以元孙。尤似未安。可疑。然丘说亦必有所据。姑阙之可也。告事条元字。岂丘氏悉改以从玄。有未能尽改者而然欤。递迁条第二十七板最长房改题祧主云云。第二十五板孝玄字义条。既曰祭主于孝。则今最长奉祀者之祭其祧主者。亦出于孝心。而独不得称孝者何耶。虽以孝字之称。不可与嫡子混而同之。其为孝于祖先者。则实无彼此之间矣。
孝之为字。子承考之义也。苟非嫡嗣承统者。恐不合称之也。如何。
最长房不能奉祧主。答说最长者既不奉祀。则恐不可以是人为主为言。然则以主人代行耶。以主人代行。亦似有嫌矣。
最长房虽不能奉祀。旁题则似不合。以别人书之。主人摄祀行之似当。世多有如是者矣。
第二十八板亲尽宗子位次。答说云云。若大宗子似不可一例看。则其位当在何行耶。抑立于众兄弟之行而少前耶。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0H 页
 来说似是。
来说似是。最长房之义。答说下方语类说末端伴五盏之伴字。是对饮之意耶。若然则未知尊丈对饮耶。私房子弟之办饮食者对饮耶。必至五盏而后罢者。亦何义耶。
伴字如今外使宴飨时接伴之义。既曰请尊长伴五盏。则似是尊长与客伴饮。既请长者为主。而自与客伴饮者。道理必不如是矣。五盏之义。即献酬礼所谓或三行或五行之例也。
第二十九板亲尽祖封勋不迁。答说中朱子答汪尚书曰云云。天子既立七庙。则其三公八命。虽仕于王朝者。宜用诸侯之礼。立五庙。有所压。故必待其出封然后。乃得立耶。
来示然矣。以汉言之。如酂侯,绛侯不得立庙。齐王,楚王可以立庙。
始勋不迁。次勋当迁。答说云云。既以庙与室果同乎为言。则其下即当明言庙与室不同之意。以解之。而今乃以立七八代龛室之不足言为结语可疑。其下方大典奉祀条云云。以别立一室之别立字看。则明是四龛之外。又立一龛。为五龛之意。正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0L 页
 与甲说为是之答。相径庭矣。
与甲说为是之答。相径庭矣。盛意认龛为室。故以此为疑。然龛与室有间。龛即是仿古之庙数者。故四龛之外。有僭上之嫌。室则不在于四数之中。故别立无妨。更详之如何。
深衣条第三十一板深衣之制问目。既有不必独以织麻为布云云之语。则答说何不举论其是非耶。尤庵先生亦用绵布为之。此亦必有所据矣。凡出于机杼者。皆名为布云云。问者之言。果是矣。然则䌷绫之属。亦非出于机杼者耶。虽用此为之。亦似无妨耶。
绵布固可通谓之布。至于绫䌷之属。帛也。恐非裁用白布之意也。若以出于机杼者而言之。则绮纨锦绣。孰非出于机杼者乎。
第三十二板裁裳之制。答说三袪缝之袪字。韵书以袖为训。若以韵书所训看。则不成文理。此袪字必是去字之义。然则所谓三袪者。指衣下裳上裳下三边。皆摺去者而言耶。其下所谓要缝半下云者。以要缝之围半于裳下之广而言耶。
三袪。疏云袪袖口也。深衣袖口尺二寸。围之为二尺四寸。而要广三其二尺四寸。为七尺二寸故云。盖谓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1H 页
 要广三其袖口也。以去字看则甚无谓。考见玉藻则可悉矣。倍要半下之义。来说是。
要广三其袖口也。以去字看则甚无谓。考见玉藻则可悉矣。倍要半下之义。来说是。居家杂仪条第三十三板教之自名。答说云云。唱喏则是揖时之声。而万福安置之礼。则行于何时耶。
丈夫唱喏。妇女道安置。此即昏定时所行之礼也。
冠礼条士冠礼。答说下方士冠礼疏事急者为先云者。指何事而言耶。贱者为先者。恐贱者易失礼。故必先之耶。昏礼则士下。即以大夫诸侯天子次之。而独冠礼。脱大夫者何耶。
周礼献官则以事之紧急者为先。故曰急者为先。仪礼行事则由士始而士贱。故曰贱者为先。冠之由士始。非以其易失礼而然也。古者五十而爵。二十而冠。何大夫冠礼之有。其冠也。服士服行士礼而已。虽天子诸侯之礼。亦不过依仿士礼而作耳。
第三十四板三加冠服。答说云云。问目并举冠服。而答说只言冠而不论服。何耶。初再三加。以程冠笠子儒巾为次者。亦有轻重之等耶。若有轻重之等。则笠子是我国之新制。而乃在儒巾之上。何耶。抑以终加为重之意耶。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1L 页
 言冠而不言服。岂文不备而然耶。然周礼爵弁服皮弁服。皆以冠而为名。无乃举冠而服在其中耶。且所着冠服。三加弥尊。则再加笠子。三加儒巾者。盖以笠子为轻。儒巾为重。以终为重之示。诚然矣。
言冠而不言服。岂文不备而然耶。然周礼爵弁服皮弁服。皆以冠而为名。无乃举冠而服在其中耶。且所着冠服。三加弥尊。则再加笠子。三加儒巾者。盖以笠子为轻。儒巾为重。以终为重之示。诚然矣。第三十五板字冠者。答说下方叶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云云。名之云者。是定名之谓耶。呼名之谓耶。若以呼名为然。则孔门群弟。皆是已冠者。而孔子呼必以名而不以字。何耶。
礼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至冠则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之。父亦不得名焉。由观则似是呼名之谓。盖子生三月。父定其名。仍以呼之也。孔门弟子之呼名不呼字。果与礼说不同。可疑。窃意冠字死谥。即周礼之弥文也。自殷以上。则虽尧舜禹汤。皆名而不字。夫子殷人也。尚质而不尚文故耶。姑不敢质言。
男女嫁娶。答说下方家语不是过也云者。此非过时不昏之谓耶。嫁娶必行于二十三十之前。而不踰于二十三十之外之谓耶。以内则注嫁必止于二十。娶必止于三十等语看。则似是不踰于二十三十外之意也。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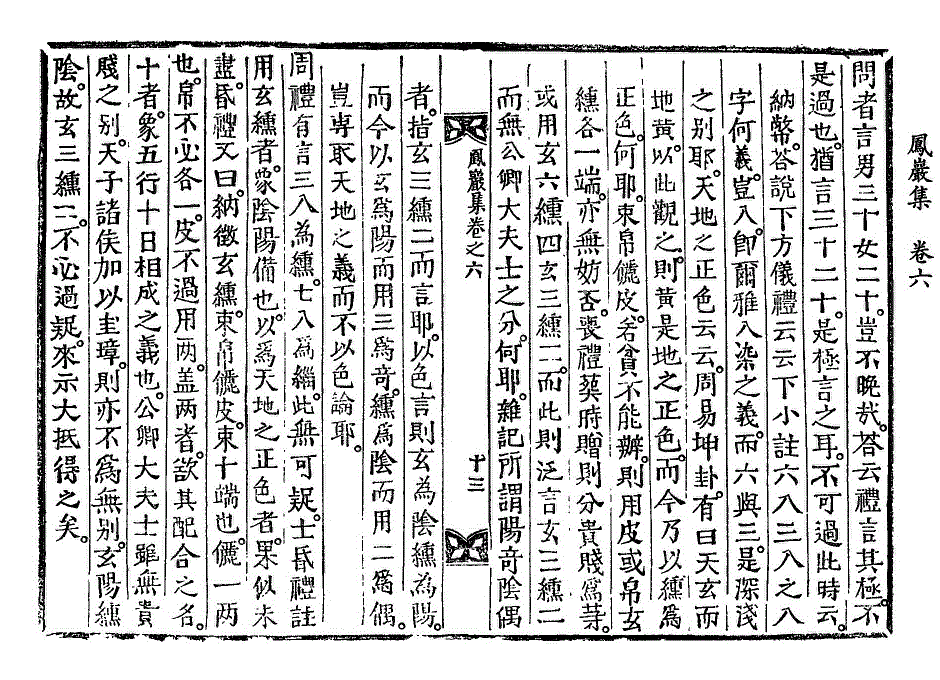 问者言男三十女二十。岂不晚哉。答云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犹言三十二十。是极言之耳。不可过此时云。
问者言男三十女二十。岂不晚哉。答云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犹言三十二十。是极言之耳。不可过此时云。纳币。答说下方仪礼云云下小注六入三入之入字何义。岂入。即尔雅入染之义。而六与三。是深浅之别耶。天地之正色云云。周易坤卦。有曰天玄而地黄。以此观之。则黄是地之正色。而今乃以纁为正色。何耶。束帛俪皮。若贫不能办。则用皮或帛玄纁各一端。亦无妨否。丧礼葬时赠则分贵贱为等。或用玄六纁四玄三纁二。而此则泛言玄三纁二而无公卿大夫士之分。何耶。杂记所谓阳奇阴偶者。指玄三纁二而言耶。以色言则玄为阴纁为阳。而今以玄为阳而用三为奇。纁为阴而用二为偶。岂专取天地之义而不以色论耶。
周礼有言三入为纁。七入为缁。此无可疑。士昏礼注用玄纁者。象阴阳备也。以为天地之正色者。果似未尽。昏礼又曰。纳徵玄纁。束帛俪皮。束十端也。俪一两也。帛不必各一。皮不过用两。盖两者。欲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之义也。公卿大夫士虽无贵贱之别。天子诸侯加以圭璋。则亦不为无别。玄阳纁阴。故玄三纁二。不必过疑。来示大抵得之矣。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2L 页
 第三十八板帔制。答说下方会通纳币章。一品所着霞帔。则不用染色之物。只庶民染色着之。而或蓝或青或素耶。素则是不染者。似与一品相混矣。庶民所着。则何其多色而无一定者耶。所谓霞帔金露帔者。其色何如。而制作亦何如。
第三十八板帔制。答说下方会通纳币章。一品所着霞帔。则不用染色之物。只庶民染色着之。而或蓝或青或素耶。素则是不染者。似与一品相混矣。庶民所着。则何其多色而无一定者耶。所谓霞帔金露帔者。其色何如。而制作亦何如。帔者。本非古制。自晋以后始有之。而所谓霞帔者。命妇之服。非恩赐。不得服。而其色亦非纯白。其制不可以详也。试以辑览所图者见之。则其长着地而阔袖大带。袖口有缘。考见之如何。
第三十九板贽币。答说下方士昏礼坐抚授人。必有其义而不能解破。可郁。家礼以改用币为定。而今人多用榛栗脯脩者。果何如耶。
舅尊。不敢授。而亦不可置之而已。故舅则坐抚之。而姑则亲举之。若亲授之者礼也。按贽币注。玉帛禽鸟榛栗枣脩之用。不一也。由是推之。则所谓贽。亦是币也。未知绢帛榛脩并用之果合于礼意否。家礼言升奠贽币。固可疑。礼辑又曰。家礼改用币。尤可疑。如或改用绢帛。则谨敬自修之义安在也。
第四十板舅姑没后庙见。答说下方士昏礼注。若舅存姑没云云。舅若存则姑之已没者。祔于祖妣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3H 页
 龛内。故云无庙可见耶。姑之祔于祖妣者。则是宗子也。舅没。亦当入于祖庙。若是庶子则姑没。即当立别室而藏其主。何可谓之无庙可见也。可疑。妇人无庙可见之妇人字。虽删之亦可。而必添入于中间者。抑有意否。曾子曰三月云云。未知妇入三月然后。乃徒见于祢庙。又择日而设祭耶。设祭不于庙见之日。而必别择日行之者。果何义耶。其下此言云云。以奠菜为一句。祭于祢为一句。一也为一句耶。
龛内。故云无庙可见耶。姑之祔于祖妣者。则是宗子也。舅没。亦当入于祖庙。若是庶子则姑没。即当立别室而藏其主。何可谓之无庙可见也。可疑。妇人无庙可见之妇人字。虽删之亦可。而必添入于中间者。抑有意否。曾子曰三月云云。未知妇入三月然后。乃徒见于祢庙。又择日而设祭耶。设祭不于庙见之日。而必别择日行之者。果何义耶。其下此言云云。以奠菜为一句。祭于祢为一句。一也为一句耶。古者无论宗子庶子。妻亡夫存。则祔于祖妣庙礼也。此所谓无庙者。盖以其舅在故也。妇人二字。有亦可。无亦可。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恐别无他意也。按曾子问。曰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疏云庙见祭祢。即是一事。此小注亦云此言奠菜。即彼祭于祢一也。来谕三月庙见。又择日设祭云者。似是偶失于照勘而然也。末端三句绝云云。来说是。
席于庙奥云云。姑必与舅异面者。有传于子妇之义。故不居其位而离坐南向位耶。
生时见舅姑。舅姑别席异面。故庙见时。亦异席别面。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3L 页
 盖亦象生时也。与常祭不同礼。
盖亦象生时也。与常祭不同礼。妇盥于门外。其下疏在外沐浴云云。生见庙见。俱是见舅姑。而有盥与沐浴之异者。何耶。
沐浴则当于宿斋时。已预为之。凡祭临时。只盥手而已礼也。
妇执笲菜云云。于舅则并告奠菜。而于姑则阙之者何义。
于舅已称奠菜。故于姑不复渎告耶。或礼有所等杀。故不无详略之异耶。不敢质言。
第四十一板婿见妇之父母。答说下方士昏礼婿入门东云云。入门而必东者。不敢当客礼之义耶。质故云云。舅婿有父子之道。父子之间。无所文饰故云质耶。质者诚实也。士之相见。亦不可无诚实之意。而独父子。乃言质。何耶。以亲授与不亲授。为质与不质之分。其义何居。
士昏礼。主人出门左西面。婿入门东面奠贽云云。出门之门。内门也。入门之门。大门也。此言入门东云者。似是错看。质者。只是不以文之意也。恐别无他义。如何如何。
易服条第四十五板披发。答说行礼之家云云。知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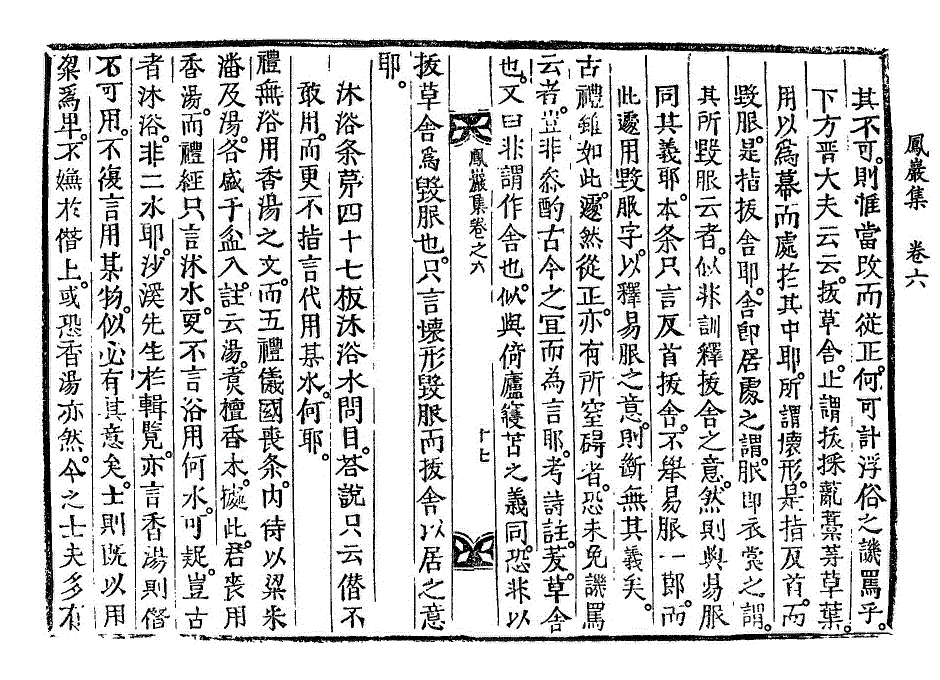 其不可。则惟当改而从正。何可计浮俗之讥骂乎。下方晋大夫云云。拔草舍。止谓拔采薍藁等草叶。用以为幕而处于其中耶。所谓坏形。是指反首。而毁服。是指拔舍耶。舍即居处之谓。服即衣裳之谓。其所毁服云者。似非训释拔舍之意。然则与易服同其义耶。本条只言反首拔舍。不举易服一节。而此遽用毁服字。以释易服之意。则断无其义矣。
其不可。则惟当改而从正。何可计浮俗之讥骂乎。下方晋大夫云云。拔草舍。止谓拔采薍藁等草叶。用以为幕而处于其中耶。所谓坏形。是指反首。而毁服。是指拔舍耶。舍即居处之谓。服即衣裳之谓。其所毁服云者。似非训释拔舍之意。然则与易服同其义耶。本条只言反首拔舍。不举易服一节。而此遽用毁服字。以释易服之意。则断无其义矣。古礼虽如此。遽然从正。亦有所窒碍者。恐未免讥骂云者。岂非参酌古今之宜而为言耶。考诗注。茇。草舍也。又曰非谓作舍也。似与倚庐寝苫之义同。恐非以拔草舍为毁服也。只言坏形毁服而拔舍以居之意耶。
沐浴条第四十七板沐浴水问目。答说只云僭不敢用。而更不指言代用某水。何耶。
礼无浴用香汤之文。而五礼仪国丧条。内侍以粱米潘及汤。各盛于盆入。注云汤。煮檀香木。据此。君丧用香汤。而礼经只言沐水。更不言浴用何水。可疑。岂古者沐浴。非二水耶。沙溪先生于辑览。亦言香汤则僭不可用。不复言用某物。似必有其意矣。士则既以用粱为卑。不嫌于僭上。或恐香汤亦然。今之士夫多有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4L 页
 用之者。其以是否。
用之者。其以是否。袭条裹肚勒帛之制问目。所谓裹肚。天益答说所谓裤管之管。是何物。而其制何如。
勒帛此条所答。只据丘仪而言之者也。其后先生又曰。丘仪如此。似未之考也。此答似非定论。盖勒帛。本非裹足之物。乃绕身之具。如大带类是也。文献通考曰。顶帽而系勒帛。勒帛亦垂绅之意。东坡诗亦曰。红线勒帛先绕胁。其制不可详也。裤管。即胫衣之两管着胫处也。何疑焉。勒帛则问解有所未详者。故敢及之。
第四十八板袭用深衣公服。答说既以礼辑为得。而又以并用古礼三称之袭为不妨。何耶。
礼辑所谓。恐碍于敛者。槩以如品带纱帽之磊巍难用者而言之也。深衣朝服则并用。亦无难者。而但未知何者为上服。今则恐不可从也。
第四十九板握手。答说下方。设决丽于掔云云。决是何物而形色何如。其用于右手者。必有其由。而既不解设决曲折。故至于握手之系与决之带馀连结之文。便有所疑晦耳。记设握裹亲肤云云。长尺二寸为句。中掩之手为句。才相对也为句耶。才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5H 页
 相对。是握之两端。堇才相连云。而语大未莹。多以手才相对看之。宜乎后世讲礼者之错认。为用一握手而系之。使两手相对而不散。其所还从上自贯云者。未知自贯于何处耶。
相对。是握之两端。堇才相连云。而语大未莹。多以手才相对看之。宜乎后世讲礼者之错认。为用一握手而系之。使两手相对而不散。其所还从上自贯云者。未知自贯于何处耶。决即决拾之决。诗注著于右手大指者也。其图在诗卷首。可考而知也。无决者。指左手而言也。长尺二寸以下句绝。来示是矣。自贯云者。还以自贯于其绕掔之系也。
袭敛设奠问目云云。东是尸之安足处。即前面也。南是尸之左手边。即傍侧也。若欲象生时。则何以舍前面而设于傍侧耶。置灵座于面而设奠于东。则魂帛与奠。又各在一处。岂朱子之始设奠于南者。是改正仪礼未尽之义耶。答说只言家礼仪礼之不可合看。而无彼此得失之分。何耶。
沐浴迁尸时。已言南首。南首者。不忍以鬼神待其亲之意也。尸东。即其当肩处。何以云尸之安足处也。南即其当首处。何以云左边傍侧也。恐失于思量而然也。人生时。如有进馔于卧所者。则当设于右边当肩处。以其始死。未忍异于生者此也。仪礼家礼。古今有异。何必强而同之也。亦岂有得失之可论者乎。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5L 页
 第八板立铭㫌。答说云云。又以图形。为其言之契左。而图形所排。则反与问目中语相合。第设帏得失。较差矣。
第八板立铭㫌。答说云云。又以图形。为其言之契左。而图形所排。则反与问目中语相合。第设帏得失。较差矣。所谓灵座之右灵床之西尸柩之东。自是一处。问者之疑过也。图形则自不得不合矣。
小敛条第十一板小敛变服。答说以家礼散垂。谓与仪礼不同。而其所以不同之义。未能揣知。
腰绖。仪礼言三日绞垂。盖谓小敛日散垂。成服日。乃绞之也。至启殡又散。既葬乃绞。而朱子于家礼成服条。有散垂之文。而不言其绞垂之时。先辈以为阙文也。又于答胡伯量书曰。绖带则两头皆散垂之。似谓成服后仍以散垂。故先辈又以为疑初年未定之论。此所谓家礼与仪礼不同者。指此而言也。然沙溪先生不欲明言之者。岂有其意耶。
第十二板妇人簪。答说下方仪礼说始死云云。箭笄是斩衰之服。则妾为君之长子。亦斩衰而独不着何耶。斩衰亦有轻重而然耶。妇人云云。既以有首为太饰而折其吉笄。则彼恶笄虽与吉笄有所美恶之不同。其有首而为饰则一也。若以太饰。折其吉笄之首。则恶笄亦何用。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6H 页
 妾为君之长子。不着箭笄者。来教似是。吉笄折首。而恶笄有首者。木笄虽有首。不为太饰。吉笄则既以象骨为之。而又不折首。则与常时何异。其意不过如此而已。
妾为君之长子。不着箭笄者。来教似是。吉笄折首。而恶笄有首者。木笄虽有首。不为太饰。吉笄则既以象骨为之。而又不折首。则与常时何异。其意不过如此而已。第十三板布头巾。答说缞巾孝巾。皆是头巾。而丧冠是屈冠也。礼之有缞巾。盖为秃者设也。而今人皆着之何耶。
古礼虽无布巾之文。世俗通用已久。且无所妨。恐不可以丘仪而遽废之也。
第十四板环绖。答说下方杂记。只言公大夫士而不言卿。何耶。丘氏说所谓侇堂之前之前字。以文势见之。是预先之意而非前面之谓。则未知所谓侇堂。是指小敛后设侇衾而殡于堂中之节而言耶。
既言公大夫则卿在其中矣。侇堂云云。来说得矣。
第十七板主人拜宾时位东向西。答说及士丧礼。晓然无疑。而但曲礼所云平常无吊宾时升降。独不由阼阶。则升降由何阶耶。
有宾则不得不升自阼阶。无宾则升降不由阼阶。盖以不忍代亲在主人之位故也。既不由阼阶。则其由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6L 页
 西阶可知。
西阶可知。第十八板小敛奠。士丧礼云云。葬前无拜礼。是其一于哀戚。不暇为礼节耶。然则遍拜谢宾。何其烦缛耶。
葬前无拜云者。孝子常侍尸柩之前。故朝夕哭。不拜之谓也。大小敛启殡遍拜者。谢宾之来吊者也。其意自别。无乃看作一件事而有此疑耶。
大敛条第二十板合两敛为一云者。设布绞小敛。将入棺。乃结之为大敛耶。然则敛何有九绞五绞之文。两衾俱用云云。其承荐之一衾。为始死所用者。则其一未知何衾。
合两敛为一。本书仪也。家礼则有曰小敛者曰大敛者。而但大敛无设绞之文。似是只行小敛。故先辈亦疑之。或言大敛条下掩首结绞云者。似以小敛时。不掩首未结绞。至是始掩而结之也。正与来意同。卷首图。虽有大小敛布绞。而大敛绞数太多。下注又言就敛于棺中。与本文不相应。其非朱子之本意。可知也。两衾云云。一是覆尸者。一似是新制有绵者也。
第二十一板涂殡。以柒棺未乾。废不用。而二十二板。又引伯量之言不柒不灰之棺。不可围以砖土。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7H 页
 两说径庭。何耶。
两说径庭。何耶。涂殡则棺柒难乾。且未柒之棺。易致伤败。故废而不用云。未见其为径庭也。
殇丧第二十四板大棺。何物。
按礼曰。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此所谓大棺者。非椁之谓欤。
斩衰条第三十七板司马操之言。未能分明解见。岂景则自立后日计而终三年之期。甲妇女则先除而不居于吉宅耶。
司马操之言。细看则可悉。盖谓乙之子景。当以出后日。为制服之始。而终三年之期也。今世此义不明。或有名为服丧而旬月即除者。或有称以心丧而巧避人言者。礼防之坏乱。彝伦之斁丧。莫此为甚。知礼之家不悟其非。良可寒心。甲之妇女先除宜矣。未亡嫠居。何必吉宅。
第四十一板承重服。答只曰先儒所论。详著于左。而无指一之语。先儒所论各异矣。岂孙曾妻。皆服三年。而玄孙妻。则只服本服为断之意耶。
诸说虽多。最后者当为定论。况于小注中以退溪所引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为的确明證。则岂非指一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7L 页
 之语耶。玄孙之妻。自当从服。此则本无可疑者。
之语耶。玄孙之妻。自当从服。此则本无可疑者。杖期条第六十三板既许出母有服。而庾蔚之以率情制服。非钟毓。何耶。其下又于出母嫁母无轻重之答。有所云云。出母嫁母有服无服。终无适莫之论。何耶。
礼为出母服杖期。而为父后者无服。疏为父后者不丧出母。重宗祀也。钟毓为父后而率情制服。废其所后者之祭。蔚之非之是也。嫁母则仪礼无服。皇朝制及国制。服与出母同。而朱子以仪礼之无服。谓举重而见轻也。其意可知。周制。父卒继母嫁。犹为之服。况所生之母乎。细考之如何。
第六十四板慈母既无天属之爱则为三年。与父在杖期。同于嫡母。何耶。
以父命为重也。
第六十五板所后母被出者云云。父之妻为母。继母之出。无生我之恩。而不成为母。不服之似当。而以有服无服。有此云云。可疑。
为父后者。所生母出。犹不服。况为人后者。所后母出。何服之有。此无可疑者。
不杖期条第二板无夫与子父母服制。问目所谓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8H 页
 本服。三年之谓耶。答说引仪礼而曰。当为期。而结辞之还相为期字义。何未莹耶。是谓侄与兄弟降为大功。则自然为期于父母也。而还相字可疑。
本服。三年之谓耶。答说引仪礼而曰。当为期。而结辞之还相为期字义。何未莹耶。是谓侄与兄弟降为大功。则自然为期于父母也。而还相字可疑。所谓本服。非三年也。乃期年之谓也。女子虽反。不绝于夫氏。故于其父母。犹服本服期而已。字义自分明矣。侄与兄弟则本服期。而以其出嫁故。降至大功。今则还相为期云尔。似无可疑。
第四板妾服问答丧服注降之则嫌。嫌之义。欲详知矣。服女君之党。终莫知其义。通典荀讷之言。解见其语。而未能解见其义矣。
降之则嫌。嫌其不相亲爱也。此外更有何嫌。来教荀讷之言解见其语而未能解见其义者。可疑。如能解其语。则义亦不难解矣。盖以妾之从服女君之党者。正如近臣君服斯服之义也。所谓君服斯服者。言君有服则近臣从而服之也。更详之。君服吐。当曰(이어시던)。
齐衰三月条第七板大传注齐衰三月。指大宗之子也。为绝族者五世外。不能解知文义。
五世外。犹言虽五世之外之意。外下吐。亦当曰五世外(나도)。
小功条第十板嫁母党服。所引吴氏说曰自应服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8L 页
 之。而曰其党不同。何耶。嫡母为母。则母生母死何异。而母死不服。何义。
之。而曰其党不同。何耶。嫡母为母。则母生母死何异。而母死不服。何义。答说若曰嫁母出母服既无异。则嫁母党出母党。岂有不同之理云尔。正与吴说自应服之者合。其党不同下吐。亦当以(이)看如何。盛意似以(이니)看故有此疑也。妾子之为嫡母党服者。亦是君服斯服之义。故嫡母死则不服。若承重妾子则不然。
缌麻条第十三板稍加日数不答之。稍加日数。果是何服。
稍加日数之教。未知其为正当道理也。缌小功外。当何服。
殇服条第二十二板生月计之。则非三殇定制之义。可疑。
似当以岁计。不以月计也。
税服条第二十五板。郑玄追服。而王肃服其残月。庾蔚之以王议为未允惬。以庾说为正耶。
郑说极是。庾所谓王议容朝闻夕除。或不容成服者。正可谓百世不易之论。而今人或于父母丧。亦用王议者多。岂不寒心者耶。
变制条。以死月为准。则闻丧晚者。当一二月即除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9H 页
 耶。
耶。闻丧虽晚。亦当满月而除。更须细看。
权葬条第六十七板。既曰当用重服。则又何言杖亦当去。应服三䄵者皆服缌。宜从众子之制。可疑。
重服云者。父未葬前斩衰也。父未葬。故葬母时。亦服斩而行之礼也。若服缌则缌本无杖。去之何疑。子于前母改葬。其服亦当如众子之制。服缌而行之。盖以改葬缌。臣子妻一也。继室子亦子也。其服安得不与众子同也。
虞条第一板。初虞用日中。既葬。安神为急。故不可迟待明日之质明。何但曰必用辰正耶。
辰正云者。非谓辰时。犹言时之正者也。辰正有三。曰朝也夕也日中也。岂亦尚赤尚黑尚白之义耶。朝既有事。不得不以日中而祭也。礼所谓君子举事。必用辰正者此也。安神为急云云。来教是矣。
第二板尸之必用童子。盖取赤心无杂念之人也。召公为童可疑。召公之无杂念。无异童子。故以为尸。非召公则何可必为童。
记有卿大夫将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齐衰内丧之文。非童子而为尸者。不但召公一人而已。童字之义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09L 页
 未详。岂以其赤心无伪而言之欤。
未详。岂以其赤心无伪而言之欤。卒哭条第八板。地产六谷作阳德。天产六牲作阴德。时祭。以天产为奇。以地产为偶。两说不同。何耶。
方氏。以六谷六牲之养人者而言之。特牲。以鼎俎笾豆所用之数而言之。故两说不同矣。
大祥条第二十二板。服其除服。示前丧有终矣。然后丧中着白笠白袍。无乃不可乎。愚意着平凉子。着后丧布深衣为宜。未知何如。
服其除服。礼有明文。依此行之。何妨。如以为未安。则来教云云。亦似无妨。然布深衣则恐不可以除服言。无乃太过乎。
初祖条第五十三板二世六世。何义耶。以意享之云者。是何意。
自高祖以上六世祖。上至始祖以下第二世祖。勿论几世。只设考妣二位之馔。享之以诚意而已。既不设各位之馔。故云以意享之而已。
续问解袭条第十三板。既用掩。又用女帽可疑。况女帽非古乎。朋友含礼既有言。而答以刱开似难。何耶。
女帽及掩。岂有并用之理。况女帽本非礼冠乎。朋友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0H 页
 之含礼虽有言。今难猝变从古。
之含礼虽有言。今难猝变从古。题主条父子俱亡问答。礼有显辟之文。则舍其妻而以女子子书之如何。显辟亡子与显兄亡从子。果何得失。
礼有女无奉祀之文。故世多以其弟若侄书之者。然愚意宗统至重。不宜代以别人。不如书以显辟之为无弊。然先代题主。则亦未知何以书之为得当也。书以女子。尤无谓。
居丧杂仪条第六十五板。入庙带。本族重丧。着黑带。果是权而得中耶。
先生亦于服中入庙时。带黑带矣。
答玉所(近思录疑义)
第四板。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先儒曰。这定与静字。正如大学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之意矣。然则圣人之于静时。岂无所用工耶。朱子又曰。圣人定其性而主于静。则当其静时。亦有个敬工而已。非敬。何以体立。亦何以酬酢万变而一天下之动哉。看此则可以见向也论静之得失矣。
第六板几善恶。几者。动之微也。昔赵致道尝有几善恶图。以善为直出。以恶为旁生。比之于宗孽主客。胡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0L 页
 氏图则以善书之于几之左。以恶书之于几之右。有若东西相对者然。未知孰是。而愚意则赵胜矣。
氏图则以善书之于几之左。以恶书之于几之右。有若东西相对者然。未知孰是。而愚意则赵胜矣。第八板一阳复于下。乃天地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大抵要见天地之心。必于动之端。求之复卦之下爻为一阳初动之端。则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矣。然则先儒之以静为见天地之心者。固非矣。然若专以静言之。则这静中。亦自有天地之心。何也。朱子尝以静字属之于坤卦。坤是纯阴之象而为十月也。十月积阴之时。犹不为无阳。而天地生物之心。固自在矣。正如人心至静之中。犹不无涵动意思而为酬酢万变之根本也。故先儒以坤言静。然则妄意于静之中。虽不可以见天地之心。而可以知其有天地之心矣。其所以不见者何也。但无端倪可见故耳。
第十三板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注。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越。椒之性。岂本恶也。莫非气质为然也。
程子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注。善恶由分。此亦理之所有。朱子又答邵浩之书曰。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只作合字看。(朱子说止此。)然则前后所释。非必谓实理有善有恶也。言其理势之有如此者云云。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1H 页
 如是看来。则不必深致疑于程子所训也。
如是看来。则不必深致疑于程子所训也。第十四板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谓不中不远。与大学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之训。旨意迥别矣。
第十五板所谓腔子云云。更详之。此腔子。是指一身之躯壳而言。非谓方寸之地也。如肢体之被刺。便即觉痛者。可以见恻隐之心。充满无欠阙处。昔有人问腔子外是甚底。退溪先生曰。这亦是恻隐之心。善哉言乎。以此推之。则不但一身躯壳之外。凡盈天地之间者。无非此心。如闻千万里之外。一有哀矜恻怛之事。则人莫不怵惕悲怜者。正由此也。是知所谓腔子。不可作方寸看。而专指躯壳而言也。
与韩德昭(元震○壬辰)
未发知觉之说。来谕以朱先生以复为比者。为初年未定之论。而考语类。安卿问答。的在庚戌己未两年。则此实先生晚年语。而亦在或问已成之后。此切可疑。如愚末学。不敢轻加取舍于先圣之论。姑欲两存其义。以俟异日万一识进之时矣。今承回教。断然以为记录之误。愚者之疑。盖已去十八九矣。甚甚幸幸。第未知尤庵先生一生学问。祖述考亭。而至其晚年。亦尝以此问答。举似于学者何哉。(答尹拯及权諰书可考。)于此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1L 页
 明白说破。则区区此心。庶无二歧之惑矣。幸卒垂教也。尤翁答尹书曰。坤与复。虽有未动已动之殊。而俱在大冬之中。心虽有未有知觉已有知觉之别。而皆不涉于喜怒。故俱在未发之前。然细分之。则但有知觉而未有所知觉。正如坤卦不能无阳云云。详此语意。则其以以复为比者。为大分说也明矣。朱先生亦尝曰。子思只说喜怒哀乐。今却转向见闻上(即知觉上)去。所以说得愈多。愈见支离。此亦大分说也。今若细推。其至静时则至虚至寂。虽鬼神有不能窥其际者。岂但以不喜不怒时节。泛然说到而已乎。朱,宋二先生此等说话。皆与平日所论未发之体。大相不同。不可不细究。幸勿专咎于记者而更加商确。以牗昏迷。千万至望。前禀鄙说上顷数处知觉上。着一所字。不能与所之所字相杂。故看者易以生疑。抹去似好。
明白说破。则区区此心。庶无二歧之惑矣。幸卒垂教也。尤翁答尹书曰。坤与复。虽有未动已动之殊。而俱在大冬之中。心虽有未有知觉已有知觉之别。而皆不涉于喜怒。故俱在未发之前。然细分之。则但有知觉而未有所知觉。正如坤卦不能无阳云云。详此语意。则其以以复为比者。为大分说也明矣。朱先生亦尝曰。子思只说喜怒哀乐。今却转向见闻上(即知觉上)去。所以说得愈多。愈见支离。此亦大分说也。今若细推。其至静时则至虚至寂。虽鬼神有不能窥其际者。岂但以不喜不怒时节。泛然说到而已乎。朱,宋二先生此等说话。皆与平日所论未发之体。大相不同。不可不细究。幸勿专咎于记者而更加商确。以牗昏迷。千万至望。前禀鄙说上顷数处知觉上。着一所字。不能与所之所字相杂。故看者易以生疑。抹去似好。答韩德昭(甲午)
前后示谕。谨悉巍友之保无他意。更何待勤教而知之。向时失言。闻甚愧服。为幸大矣。义理之烂熳同归。已无可望。各守所见。日迈月征。庸何伤乎。但闻洛中嚣嚣之言。比来转剧。甚可怕也。理无不善。而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故单言理则有善无恶。兼言气则有善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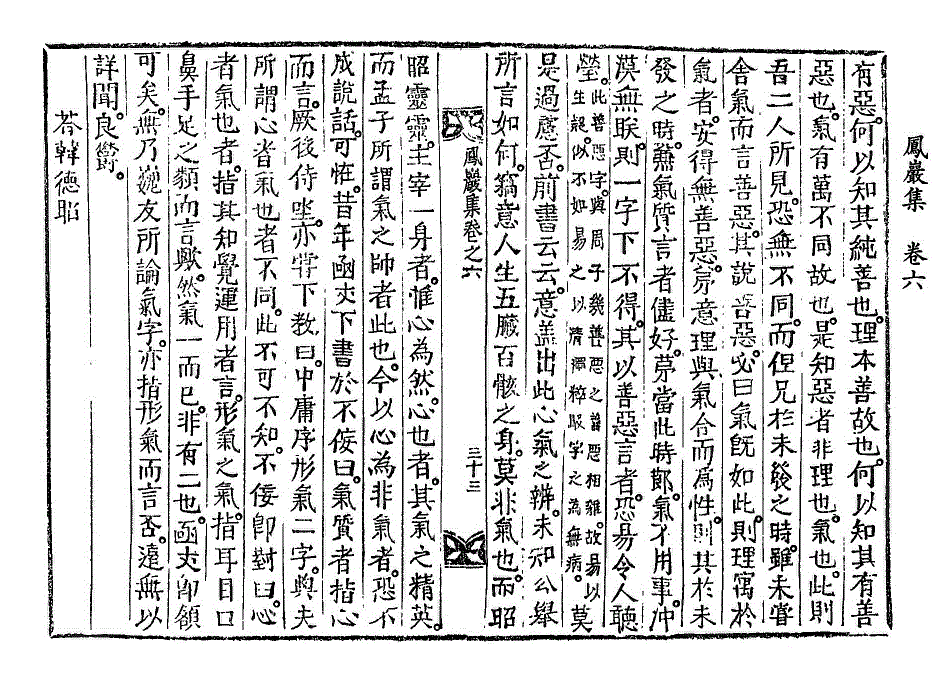 有恶。何以知其纯善也。理本善故也。何以知其有善恶也。气有万不同故也。是知恶者非理也。气也。此则吾二人所见。恐无不同。而但兄于未发之时。虽未尝舍气而言善恶。其说善恶。必曰气既如此。则理寓于气者。安得无善恶。弟意理与气合而为性。则其于未发之时。兼气质言者尽好。第当此时节。气不用事。冲漠无眹。则一字下不得。其以善恶言者。恐易令人听莹。(此善恶字。与周子几善恶之善恶相杂。故易以生疑。似不如易之以清浊粹驳字之为无病。)莫是过虑否。前书云云。意盖出此心气之辨。未知公举所言如何。窃意人生五脏百骸之身。莫非气也。而昭昭灵灵。主宰一身者。惟心为然。心也者。其气之精英。而孟子所谓气之帅者此也。今以心为非气者。恐不成说话。可怪。昔年函丈下书于不佞曰。气质者指心而言。厥后侍坐。亦尝下教曰。中庸序形气二字。与夫所谓心者气也者不同。此不可不知。不佞即对曰。心者气也者。指其知觉运用者言。形气之气。指耳目口鼻手足之类而言欤。然气一而已。非有二也。函丈即颔可矣。无乃巍友所论气字。亦指形气而言否。远无以详闻。良郁。
有恶。何以知其纯善也。理本善故也。何以知其有善恶也。气有万不同故也。是知恶者非理也。气也。此则吾二人所见。恐无不同。而但兄于未发之时。虽未尝舍气而言善恶。其说善恶。必曰气既如此。则理寓于气者。安得无善恶。弟意理与气合而为性。则其于未发之时。兼气质言者尽好。第当此时节。气不用事。冲漠无眹。则一字下不得。其以善恶言者。恐易令人听莹。(此善恶字。与周子几善恶之善恶相杂。故易以生疑。似不如易之以清浊粹驳字之为无病。)莫是过虑否。前书云云。意盖出此心气之辨。未知公举所言如何。窃意人生五脏百骸之身。莫非气也。而昭昭灵灵。主宰一身者。惟心为然。心也者。其气之精英。而孟子所谓气之帅者此也。今以心为非气者。恐不成说话。可怪。昔年函丈下书于不佞曰。气质者指心而言。厥后侍坐。亦尝下教曰。中庸序形气二字。与夫所谓心者气也者不同。此不可不知。不佞即对曰。心者气也者。指其知觉运用者言。形气之气。指耳目口鼻手足之类而言欤。然气一而已。非有二也。函丈即颔可矣。无乃巍友所论气字。亦指形气而言否。远无以详闻。良郁。答韩德昭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2L 页
 昨夕。宋信甫归自平湖。袖致兄书。得审梅友病甚。已至难医之境。悲夫。此友之受气甚薄。已为侪流忧久矣。而所恃者。天佑善人。理不当夺之斯速也。示谕谨悉。公举疑吾兄不足上及于函丈。疑函丈不足又及于栗尤。则自栗尤以上。不见疑者。能几人。可怕。彼虽偶有所失。吾辈恐不当执而为口实。且性与天命。不足以为道则已。不然则知性知命者。岂不可谓知道乎。今之学者。于性命二字。虽有一班之见。知之既不以真。则固不可以知道目之。世苟有知性知命以至于天者。洞见大源十分真的。则虽虞舜之大知。亦无以过此。未知古圣人所知之道。于此别有一分至高至妙者乎。古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今若以此遽谓之凝道体道则诚过矣。既知之则似不得不下知字。成仲亦何所见。莫是以知道字甚重。不欲轻许于老兄而然耶。此则不为过矣。气质说。有何新密意思。第彼中诸益之犹以为疑者。窃恐听莹于未发时性善恶之说。致此纷纭。只此一段语。恐易生病。老兄虽未尝显言未发时善恶之理。窃观言论归趣。尝有此意思。故时发于语次者多矣。一以老兄所录山中记语。为公案似好。(德昭山中记语曰。未发前理则纯善。而气则有善有恶云云。故有是言。)
昨夕。宋信甫归自平湖。袖致兄书。得审梅友病甚。已至难医之境。悲夫。此友之受气甚薄。已为侪流忧久矣。而所恃者。天佑善人。理不当夺之斯速也。示谕谨悉。公举疑吾兄不足上及于函丈。疑函丈不足又及于栗尤。则自栗尤以上。不见疑者。能几人。可怕。彼虽偶有所失。吾辈恐不当执而为口实。且性与天命。不足以为道则已。不然则知性知命者。岂不可谓知道乎。今之学者。于性命二字。虽有一班之见。知之既不以真。则固不可以知道目之。世苟有知性知命以至于天者。洞见大源十分真的。则虽虞舜之大知。亦无以过此。未知古圣人所知之道。于此别有一分至高至妙者乎。古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今若以此遽谓之凝道体道则诚过矣。既知之则似不得不下知字。成仲亦何所见。莫是以知道字甚重。不欲轻许于老兄而然耶。此则不为过矣。气质说。有何新密意思。第彼中诸益之犹以为疑者。窃恐听莹于未发时性善恶之说。致此纷纭。只此一段语。恐易生病。老兄虽未尝显言未发时善恶之理。窃观言论归趣。尝有此意思。故时发于语次者多矣。一以老兄所录山中记语。为公案似好。(德昭山中记语曰。未发前理则纯善。而气则有善有恶云云。故有是言。)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3H 页
 与韩德昭
与韩德昭人生。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凝合而成者。固是阴阳五行之气。而心体本虚。灵灵昭昭者。亦莫非这个气也。气一而已。方其流行发育之初。夫岂有人与物之间。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以成形。故其心虚灵。万理咸备。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以成形。故其心不能虚灵。理无以著焉。(禽兽或有一点明者。草木全无心可说矣。)此朱先生所谓人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也。然则人之一心。是聚五行精英之气者欤。精英所聚。便自虚明。是以就身上说气。则耳听属金水。目视属木。口话属火。鼻臭属土之类。凡有血气者。不甚相远也。就心上说气。则温厚者木之气也。严肃者金之气也。宣著者火之气也。通明者水之气也。其发为爱恭宜别。而其理则仁义礼智也。是则惟人也独得其全。而物则无与焉。直由于形气之禀。有偏正通塞之不同耳。若论人心天命之本体。则均乎鉴空衡平。烱然不昧。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只为这气正通之中。亦不能无清浊粹驳之禀。各拘于有生之初。声色臭味之欲。交蔽于既生之后。或至虚者反以塞焉。至灵者反以顽然。而心之昏明强弱。于是乎有万不齐矣。然此岂心之本体然哉。人见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3L 页
 其既昏且塞也。而以为未尝虚明也。哀哉。比之火焉。火之光明者。其本体也。今虽为他所拘。未免昏暗。而其本体明。故吹得这火。便自宣著。此岂非较然易见者乎。若以此。便说火之体本自有昏明之别。则愚未敢知也。至于勉斋所谓气虽昏而理自明者。槩谓气质之禀。虽甚昏浊者。当其未发也。心体湛然。物欲不生。故本然之理。烱然自在云尔。若曰当此时节。性则明而心之本体犹不能明。则朱夫子其肯点头乎。盖未发之时。气不用事。则此心湛然。自无私欲之昏蔽。故天命之本体。烱然呈露于中矣。若有一点子昏蔽。则是气已用事也。安得谓之未发也。且气质之有善有恶。生禀之一定者也。人性之有善无恶。天理之本然也。今若以未发时气有善恶。疑于未发时理亦有善恶。则窃恐其大错。夫仁义礼智之外。更无他理。而天下之情。(虽恶情亦然。)无一不本于四者之性。方其未发时。只有此一件仁义礼智之理浑然全具而已。曷尝有恶理在。但此理堕在于气质之中。故及其气用事之时。木之气偏者发于仁者。反害于仁。金之气偏者发于义者。反害于义。礼智仿此。由是观之。未发时气虽有善恶。而理则纯善而已。要着一恶字不得。如何
其既昏且塞也。而以为未尝虚明也。哀哉。比之火焉。火之光明者。其本体也。今虽为他所拘。未免昏暗。而其本体明。故吹得这火。便自宣著。此岂非较然易见者乎。若以此。便说火之体本自有昏明之别。则愚未敢知也。至于勉斋所谓气虽昏而理自明者。槩谓气质之禀。虽甚昏浊者。当其未发也。心体湛然。物欲不生。故本然之理。烱然自在云尔。若曰当此时节。性则明而心之本体犹不能明。则朱夫子其肯点头乎。盖未发之时。气不用事。则此心湛然。自无私欲之昏蔽。故天命之本体。烱然呈露于中矣。若有一点子昏蔽。则是气已用事也。安得谓之未发也。且气质之有善有恶。生禀之一定者也。人性之有善无恶。天理之本然也。今若以未发时气有善恶。疑于未发时理亦有善恶。则窃恐其大错。夫仁义礼智之外。更无他理。而天下之情。(虽恶情亦然。)无一不本于四者之性。方其未发时。只有此一件仁义礼智之理浑然全具而已。曷尝有恶理在。但此理堕在于气质之中。故及其气用事之时。木之气偏者发于仁者。反害于仁。金之气偏者发于义者。反害于义。礼智仿此。由是观之。未发时气虽有善恶。而理则纯善而已。要着一恶字不得。如何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4H 页
 如何。
如何。答韩德昭(乙未)
示谕缕缕。深服正见之明透也。盖区区之见。本非有所径庭于高明之论。妄窃以为彼中义理之卞。已成会讼之势。苟于遣辞之际。或有一分欠明者。则适足以起闹而已。故就高明文字中。不避猥越。论證刻甚。正欲仰补其万一之罅漏。使言者无所致诘而庶几于归一也。盛教所谓实无指归之相戾者。得之矣。但各具太极一段。鄙于下语之际。忙猝未及精商。故即欲追改而远莫之能。寻常歉愧未已。今承指教。正所谓顶门上一针。钦悚钦悚。第高明于鄙意。犹有所未尽究者。故略申之。夫太极者。只是无形象方所。而不可模捉之称也。其为体也冲漠无眹。故就人物而言其理之本体。则均乎无眹而已。有何声臭之可求者也。先儒言性是太极。心为太极者。以此而已。如以人物所受之性。直作太极字看。则恐或有所未安。盖以性或不齐而太极则无不全故也。鄙见本自如此。故顷年见尹晦甫于华阳山中。言性是太极之全体者。恐亦指天命之初而说。晦甫答。若如子说。则先儒言性为太极之说非耶。鄙甚惑焉。归即驰禀于江上。则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4L 页
 下教曰。理无不全而性有偏全。性与太极不同之说然矣。小子心甚服信。而常恨向来为晦甫说者。犹欠其精详矣。顷者窃覸高见。盖与鄙意吻合。而反以各具之太极。谓不合异体上看。故鄙却以为既言各具则分明是就异体上看。妄意只欲发明其物物各具冲漠之体尔。非谓有各个太极偏全大小。随处不同也。想有以量之也。
下教曰。理无不全而性有偏全。性与太极不同之说然矣。小子心甚服信。而常恨向来为晦甫说者。犹欠其精详矣。顷者窃覸高见。盖与鄙意吻合。而反以各具之太极。谓不合异体上看。故鄙却以为既言各具则分明是就异体上看。妄意只欲发明其物物各具冲漠之体尔。非谓有各个太极偏全大小。随处不同也。想有以量之也。五常说。梅,巍二友各守所见。更无初晚之殊。而未发气质说。则曰气质者心也。心之本体。圣凡一也。当其未发也。均乎虚明。而南塘则谓人心本体。圣凡不同。故善恶相杂。此何见识。余谓气质者。血气形质也。心是这气精英处。但气质所拘。心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本体之明则未尝有异。韩友之见。本自如此。所谓铜铁精粗。屋材美恶。是指血气形质而言。非指人心本明之体也。公举言德昭云气质者心也。心之体不齐。故未发时。善恶对峙并立云。吾辈只欲发明其不然。若道人心本体。一皆虚明。而只为形质所拘。则亦何争卞之有。观其意趣。略似有变于前矣。
答韩德昭
示谕未发知觉之说。谨悉精透之见。窃详程子与苏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5H 页
 季明问答。始则曰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末又曰静中须有物。始得其言有物言存养。非敬而何。语意至精且密。无可容议。但其中间。却云耳无闻目无见。又云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此正说得太过处也。愚不敢知。七情未发之时。此心嗒然。全无所知觉。则存养持敬之工。将何以用力耶。语欠完具。前后矛盾可疑。窃尝闻程子每以敬而无失。为未发之中。此则所谓静中有物者也。又谓凡言心。皆指已发而言。此即所谓既有知觉。却是动者也。莫是先生初年所见。认心为已发。故不欲说知觉于未发之前耶。然先生晚来。因吕氏未发不可无心之语而即改其初见。向使季明还问未发不可无知觉云尔。则安知其不即改也。其不得为定论者。据此可知。至若朱夫子尝曰。方其未发而必有事焉。是乃静中之知觉。又曰。心之有知觉。如耳之有闻。目之有见。虽未发而未尝无。又曰。见个事物。心里不喜不怒。如何谓已发。此与中庸或问注。未曾着于事物。但有知觉。不妨为静者。互相发明。诚千古不易之定论也。至其答南轩书。以复当静中知觉者。虽若可疑。然实与程说。有些不同。程子则谓复之一阳已动。不得为未发。则知觉怎生言静。
季明问答。始则曰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末又曰静中须有物。始得其言有物言存养。非敬而何。语意至精且密。无可容议。但其中间。却云耳无闻目无见。又云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此正说得太过处也。愚不敢知。七情未发之时。此心嗒然。全无所知觉。则存养持敬之工。将何以用力耶。语欠完具。前后矛盾可疑。窃尝闻程子每以敬而无失。为未发之中。此则所谓静中有物者也。又谓凡言心。皆指已发而言。此即所谓既有知觉。却是动者也。莫是先生初年所见。认心为已发。故不欲说知觉于未发之前耶。然先生晚来。因吕氏未发不可无心之语而即改其初见。向使季明还问未发不可无知觉云尔。则安知其不即改也。其不得为定论者。据此可知。至若朱夫子尝曰。方其未发而必有事焉。是乃静中之知觉。又曰。心之有知觉。如耳之有闻。目之有见。虽未发而未尝无。又曰。见个事物。心里不喜不怒。如何谓已发。此与中庸或问注。未曾着于事物。但有知觉。不妨为静者。互相发明。诚千古不易之定论也。至其答南轩书。以复当静中知觉者。虽若可疑。然实与程说。有些不同。程子则谓复之一阳已动。不得为未发。则知觉怎生言静。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5L 页
 朱子之意以为复之一阳虽动。寒威闭野。万物未生。固不害于未发。则知觉何妨其为静。取比虽同。意自迥别。似与程先生专言于已发者异矣。大抵坤复二卦。虽有未动已动之殊。俱在大冬物未生之时。故先生以为无间可容息处。其为说。或有本于程子之意。然终不如以坤之不能无阳者为比。故及其见疑于择之之后。则反以坤卦当之。论性答藁后记曰。答敬夫书。亦本于程子之意。此虽未为有失。词意有未具。择之之疑虽过。然察之亦密矣。故或问。以程先生以复为比者为未可。真可谓置水不漏。然厥后陈安卿问未发之前。须常恁地醒。便是知觉否。曰。固是知觉。曰。知觉便是动否。曰。固是动。曰。何以谓之未发。曰。知觉虽是动。不害其为未发。喜怒哀乐则又别也。仍言复见天地之心。说得好。复一阳生。岂不是动。曰。一阳虽动。未发生万物。便是未发否。曰。此亦先生晚年语也。按此问答。在或问已成之后。由观先生之以坤为比者。但以能知能觉者而言也。以复为比者。以其所知所觉者而言也。知觉虽有能与所之别。俱不涉七情。故均谓之未发也。此则朱先生所见。非有初末之异。所就而言者不同故也。其以复为比者。正谓方无
朱子之意以为复之一阳虽动。寒威闭野。万物未生。固不害于未发。则知觉何妨其为静。取比虽同。意自迥别。似与程先生专言于已发者异矣。大抵坤复二卦。虽有未动已动之殊。俱在大冬物未生之时。故先生以为无间可容息处。其为说。或有本于程子之意。然终不如以坤之不能无阳者为比。故及其见疑于择之之后。则反以坤卦当之。论性答藁后记曰。答敬夫书。亦本于程子之意。此虽未为有失。词意有未具。择之之疑虽过。然察之亦密矣。故或问。以程先生以复为比者为未可。真可谓置水不漏。然厥后陈安卿问未发之前。须常恁地醒。便是知觉否。曰。固是知觉。曰。知觉便是动否。曰。固是动。曰。何以谓之未发。曰。知觉虽是动。不害其为未发。喜怒哀乐则又别也。仍言复见天地之心。说得好。复一阳生。岂不是动。曰。一阳虽动。未发生万物。便是未发否。曰。此亦先生晚年语也。按此问答。在或问已成之后。由观先生之以坤为比者。但以能知能觉者而言也。以复为比者。以其所知所觉者而言也。知觉虽有能与所之别。俱不涉七情。故均谓之未发也。此则朱先生所见。非有初末之异。所就而言者不同故也。其以复为比者。正谓方无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6H 页
 而已有。以阴而包阳。动静相涵。体用不离之妙也。似与程子怎生言静者绝异矣。说者乃云未发之时。此心全无所知觉。则除是口哑耳聋视盲心死。便作一种痴呆魍魉汉。方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可乎。且心是活物。虚灵知觉。通贯动静。为一身主宰。圣贤之心。常存敬畏。提撕警觉。无一息间断。岂有顷刻放下。冥然不省之时乎。近来看得此理似有头绪。未知吾友以为如何。释义之卞。弟非其人。何敢代斲。望兄速加考證。以惠后学。
而已有。以阴而包阳。动静相涵。体用不离之妙也。似与程子怎生言静者绝异矣。说者乃云未发之时。此心全无所知觉。则除是口哑耳聋视盲心死。便作一种痴呆魍魉汉。方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可乎。且心是活物。虚灵知觉。通贯动静。为一身主宰。圣贤之心。常存敬畏。提撕警觉。无一息间断。岂有顷刻放下。冥然不省之时乎。近来看得此理似有头绪。未知吾友以为如何。释义之卞。弟非其人。何敢代斲。望兄速加考證。以惠后学。答韩德昭
朱子以天下无性外之物。为统体一太极。以万物之各一其性。为各具一太极者。信有精义。不可草草说过。而高明则以性与太极两言对说者。似欠曲折。故妄计虑或有未尽者矣。承谕。曰性之超气言者。谓与太极无别则可。而以兼气言者。谓与太极无别则不可者。曲折甚分明。鄙见亦不过如此而已。但老兄每以统体各具。必欲就一处看者。此恐不然。夫太极者道而已。自其用之显者而观之。则乘机流行。其分虽殊。以其体之微者而言之。则精粗大小。随处浑然。朱先生所谓异中识其同者此也。然则一原处。可以言
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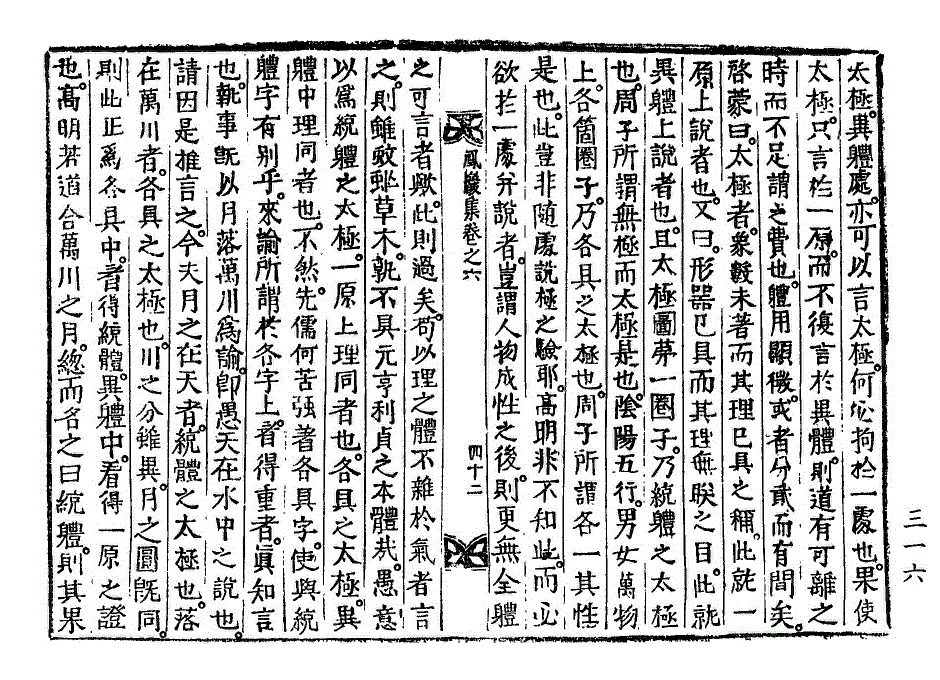 太极。异体处。亦可以言太极。何必拘于一处也。果使太极。只言于一原。而不复言于异体。则道有可离之时而不足谓之费也。体用显微。或者分贰而有间矣。启蒙曰。太极者。象数未著而其理已具之称。此就一原上说者也。又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此就异体上说者也。且太极图第一圈子。乃统体之太极也。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也。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上。各个圈子。乃各具之太极也。周子所谓各一其性是也。此岂非随处说极之验耶。高明非不知此。而必欲于一处并说者。岂谓人物成性之后。则更无全体之可言者欤。此则过矣。苟以理之体不杂于气者言之。则虽蚊虻草木。孰不具元亨利贞之本体哉。愚意以为统体之太极。一原上理同者也。各具之太极。异体中理同者也。不然。先儒何苦强着各具字。使与统体字有别乎。来谕所谓于各字上。看得重者。真知言也。执事既以月落万川为谕。即愚天在水中之说也。请因是推言之。今夫月之在天者。统体之太极也。落在万川者。各具之太极也。川之分虽异。月之圆既同。则此正为各具中。看得统体。异体中。看得一原之證也。高明若道合万川之月。总而名之曰统体。则其果
太极。异体处。亦可以言太极。何必拘于一处也。果使太极。只言于一原。而不复言于异体。则道有可离之时而不足谓之费也。体用显微。或者分贰而有间矣。启蒙曰。太极者。象数未著而其理已具之称。此就一原上说者也。又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此就异体上说者也。且太极图第一圈子。乃统体之太极也。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也。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上。各个圈子。乃各具之太极也。周子所谓各一其性是也。此岂非随处说极之验耶。高明非不知此。而必欲于一处并说者。岂谓人物成性之后。则更无全体之可言者欤。此则过矣。苟以理之体不杂于气者言之。则虽蚊虻草木。孰不具元亨利贞之本体哉。愚意以为统体之太极。一原上理同者也。各具之太极。异体中理同者也。不然。先儒何苦强着各具字。使与统体字有别乎。来谕所谓于各字上。看得重者。真知言也。执事既以月落万川为谕。即愚天在水中之说也。请因是推言之。今夫月之在天者。统体之太极也。落在万川者。各具之太极也。川之分虽异。月之圆既同。则此正为各具中。看得统体。异体中。看得一原之證也。高明若道合万川之月。总而名之曰统体。则其果凤岩集卷之六 第 317H 页
 合于图解分合之义耶。文元先生曰。有统体一太极。有各具一太极。理尽则物尽者。指人与物。各具一太极也。若统体之太极。则无终始无死生矣。此实为统体各具之分。更乞详之。鄙意本不以粗浅者为太极之体下句。两便是字。实程子洒扫应对。便是形上之意。便是即不离之义。各指物理而言。则木专于仁。金专于义。然太极之体。固未尝外此。未知此外何处。寻看太极之体耶。朱子曰。笾豆器数之末。道之全体。无所不该。此正所谓不杂不离之妙也。木虽专仁。金虽专义。然元亨利贞之全体浑然。不可须臾离也。故理之外。别无以见太极。而来谕以理与太极。分析过甚。无乃矫枉过直而然耶。夫天地。道中之一物。以天地视人物。大小虽迥别。其为物则一而已。其不可以形体之大小。各相为统体也明矣。不审高明何言之及此。愚尝以为外阴阳而别求太极。则太极入于空虚。以阴阳而看作太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观乎此则区区之见。略识其梗槩矣。
合于图解分合之义耶。文元先生曰。有统体一太极。有各具一太极。理尽则物尽者。指人与物。各具一太极也。若统体之太极。则无终始无死生矣。此实为统体各具之分。更乞详之。鄙意本不以粗浅者为太极之体下句。两便是字。实程子洒扫应对。便是形上之意。便是即不离之义。各指物理而言。则木专于仁。金专于义。然太极之体。固未尝外此。未知此外何处。寻看太极之体耶。朱子曰。笾豆器数之末。道之全体。无所不该。此正所谓不杂不离之妙也。木虽专仁。金虽专义。然元亨利贞之全体浑然。不可须臾离也。故理之外。别无以见太极。而来谕以理与太极。分析过甚。无乃矫枉过直而然耶。夫天地。道中之一物。以天地视人物。大小虽迥别。其为物则一而已。其不可以形体之大小。各相为统体也明矣。不审高明何言之及此。愚尝以为外阴阳而别求太极。则太极入于空虚。以阴阳而看作太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观乎此则区区之见。略识其梗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