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讲义
讲义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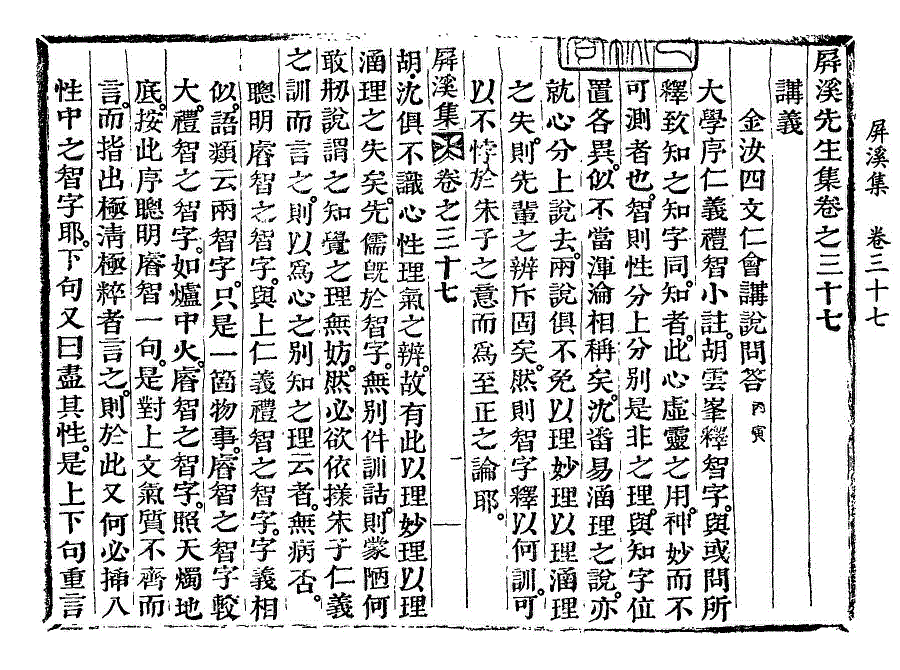 金汝四文仁会讲说问答(丙寅)
金汝四文仁会讲说问答(丙寅)大学序仁义礼智小注。胡云峰释智字。与或问所释致知之知字同。知者。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智则性分上分别是非之理。与知字位置各异。似不当浑沦相称矣。沈番易涵理之说。亦就心分上说去。两说俱不免以理妙理以理涵理之失。则先辈之辨斥固矣。然则智字释以何训。可以不悖于朱子之意而为至正之论耶。
胡,沈俱不识心性理气之辨。故有此以理妙理以理涵理之失矣。先儒既于智字。无别件训诂。则蒙陋何敢刱说谓之知觉之理无妨。然必欲依㨾朱子仁义之训而言之。则以为心之别知之理云者。无病否。
聪明睿智之智字。与上仁义礼智之智字。字义相似。语类云两智字。只是一个物事。睿智之智字较大。礼智之智字。如炉中火。睿智之智字。照天烛地底。按此序聪明睿智一句。是对上文气质不齐而言。而指出极清极粹者言之。则于此又何必插入性中之智字耶。下句又曰尽其性。是上下句重言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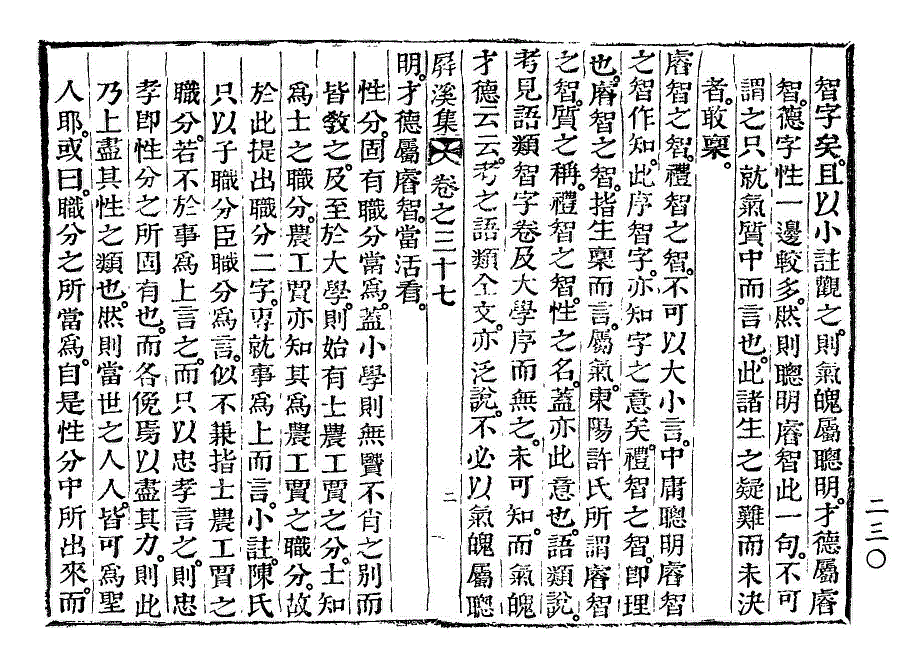 智字矣。且以小注观之。则气魄属聪明。才德属睿智。德字性一边较多。然则聪明睿智此一句。不可谓之只就气质中而言也。此诸生之疑难而未决者。敢禀。
智字矣。且以小注观之。则气魄属聪明。才德属睿智。德字性一边较多。然则聪明睿智此一句。不可谓之只就气质中而言也。此诸生之疑难而未决者。敢禀。睿智之智。礼智之智。不可以大小言。中庸聪明睿智之智作知。此序智字。亦知字之意矣。礼智之智。即理也。睿智之智。指生禀而言。属气。东阳许氏所谓睿智之智。质之称。礼智之智。性之名。盖亦此意也。语类说。考见语类智字卷及大学序而无之。未可知。而气魄才德云云。考之语类全文。亦泛说。不必以气魄属聪明。才德属睿智。当活看。
性分。固有职分当为。盖小学则无贤不肖之别而皆教之。及至于大学。则始有士农工贾之分。士知为士之职分。农工贾亦知其为农工贾之职分。故于此提出职分二字。专就事为上而言。小注。陈氏只以子职分臣职分为言。似不兼指士农工贾之职分。若不于事为上言之。而只以忠孝言之。则忠孝即性分之所固有也。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则此乃上尽其性之类也。然则当世之人人。皆可为圣人耶。或曰。职分之所当为。自是性分中所出来。而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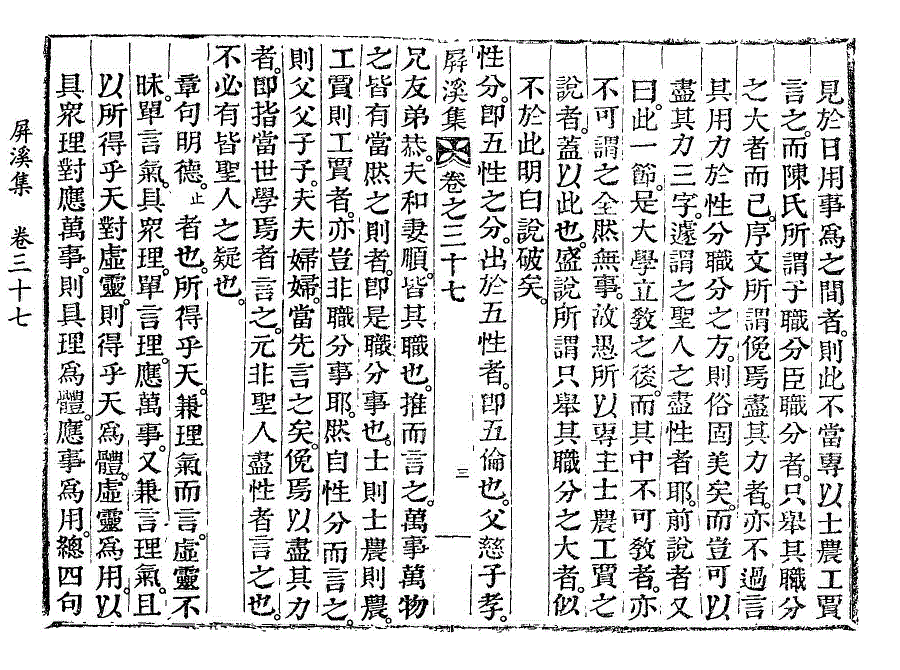 见于日用事为之间者。则此不当专以士农工贾言之。而陈氏所谓子职分臣职分者。只举其职分之大者而已。序文所谓俛焉尽其力者。亦不过言其用力于性分职分之方。则俗固美矣。而岂可以尽其力三字。遽谓之圣人之尽性者耶。前说者又曰。此一节。是大学立教之后。而其中不可教者。亦不可谓之全然无事。故愚所以专主士农工贾之说者。盖以此也。盛说所谓只举其职分之大者。似不于此明白说破矣。
见于日用事为之间者。则此不当专以士农工贾言之。而陈氏所谓子职分臣职分者。只举其职分之大者而已。序文所谓俛焉尽其力者。亦不过言其用力于性分职分之方。则俗固美矣。而岂可以尽其力三字。遽谓之圣人之尽性者耶。前说者又曰。此一节。是大学立教之后。而其中不可教者。亦不可谓之全然无事。故愚所以专主士农工贾之说者。盖以此也。盛说所谓只举其职分之大者。似不于此明白说破矣。性分。即五性之分。出于五性者。即五伦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皆其职也。推而言之。万事万物之皆有当然之则者。即是职分事也。士则士农则农。工贾则工贾者。亦岂非职分事耶。然自性分而言之。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当先言之矣。俛焉以尽其力者。即指当世学焉者言之。元非圣人尽性者言之也。不必有皆圣人之疑也。
章句明德。(止)者也。所得乎天。兼理气而言。虚灵不昧。单言气。具众理。单言理。应万事。又兼言理气。且以所得乎天对虚灵。则得乎天为体。虚灵为用。以具众理对应万事。则具理为体。应事为用。总四句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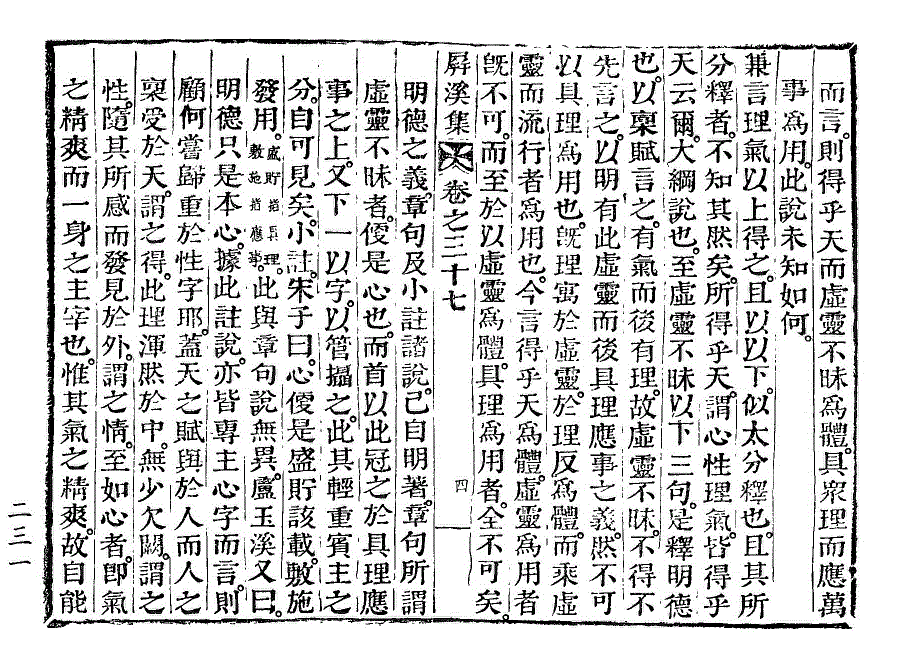 而言。则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为体。具众理而应万事为用。此说未知如何。
而言。则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为体。具众理而应万事为用。此说未知如何。兼言理气以上得之。且以以下。似太分释也。且其所分释者。不知其然矣。所得乎天。谓心性理气。皆得乎天云尔。大纲说也。至虚灵不昧以下三句。是释明德也。以禀赋言之。有气而后有理。故虚灵不昧。不得不先言之。以明有此虚灵而后具理应事之义。然不可以具理为用也。既理寓于虚灵。于理反为体。而乘虚灵而流行者为用也。今言得乎天为体。虚灵为用者既不可。而至于以虚灵为体。具理为用者。全不可矣。
明德之义。章句及小注诸说。已自明著。章句所谓虚灵不昧者。便是心也。而首以此冠之于具理应事之上。又下一以字。以管摄之。此其轻重宾主之分。自可见矣。小注。朱子曰。心便是盛贮该载。敷施发用。(盛贮指具理。敷施指应事。)此与章句说无异。卢玉溪又曰。明德只是本心。据此注说。亦皆专主心字而言。则顾何尝归重于性字耶。盖天之赋与于人而人之禀受于天。谓之得。此理浑然于中。无少欠阙。谓之性。随其所感而发见于外。谓之情。至如心者。即气之精爽而一身之主宰也。惟其气之精爽。故自能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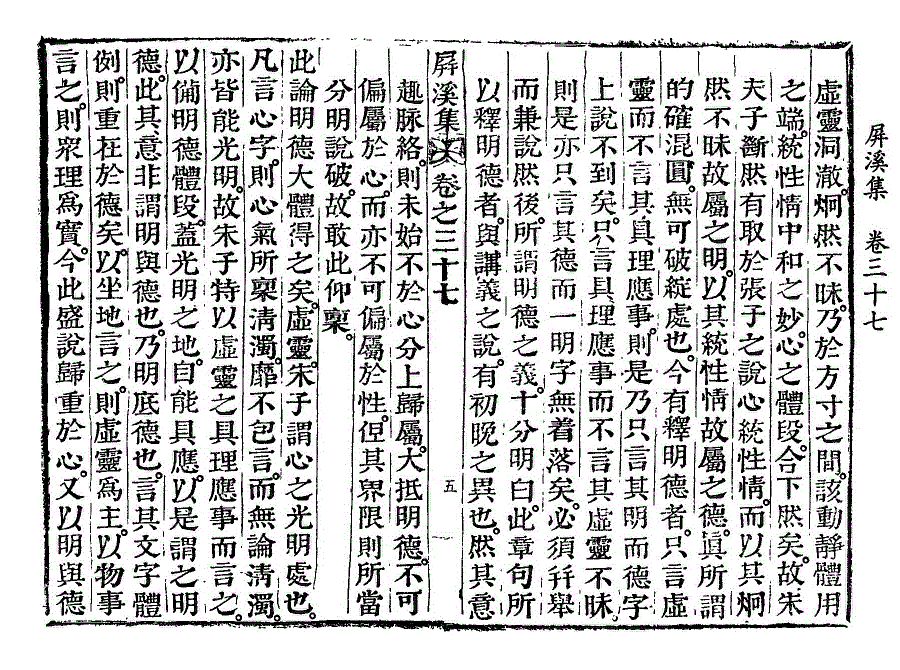 虚灵洞澈。炯然不昧。乃于方寸之间。该动静体用之端。统性情中和之妙。心之体段。合下然矣。故朱夫子断然有取于张子之说心统性情。而以其炯然不昧故属之明。以其统性情故属之德。真所谓的确混圆。无可破绽处也。今有释明德者。只言虚灵而不言其具理应事。则是乃只言其明而德字上说不到矣。只言具理应事而不言其虚灵不昧。则是亦只言其德而一明字无着落矣。必须并举而兼说然后。所谓明德之义。十分明白。此章句所以释明德者。与讲义之说。有初晚之异也。然其意趣脉络。则未始不于心分上归属。大抵明德。不可偏属于心。而亦不可偏属于性。但其界限则所当分明说破。故敢此仰禀。
虚灵洞澈。炯然不昧。乃于方寸之间。该动静体用之端。统性情中和之妙。心之体段。合下然矣。故朱夫子断然有取于张子之说心统性情。而以其炯然不昧故属之明。以其统性情故属之德。真所谓的确混圆。无可破绽处也。今有释明德者。只言虚灵而不言其具理应事。则是乃只言其明而德字上说不到矣。只言具理应事而不言其虚灵不昧。则是亦只言其德而一明字无着落矣。必须并举而兼说然后。所谓明德之义。十分明白。此章句所以释明德者。与讲义之说。有初晚之异也。然其意趣脉络。则未始不于心分上归属。大抵明德。不可偏属于心。而亦不可偏属于性。但其界限则所当分明说破。故敢此仰禀。此论明德大体得之矣。虚灵。朱子谓心之光明处也。凡言心字。则心气所禀清浊。靡不包言。而无论清浊。亦皆能光明。故朱子特以虚灵之具理应事而言之。以备明德体段。盖光明之地。自能具应。以是谓之明德。此其意非谓明与德也。乃明底德也。言其文字体例。则重在于德矣。以坐地言之。则虚灵为主。以物事言之。则众理为实。今此盛说归重于心。又以明与德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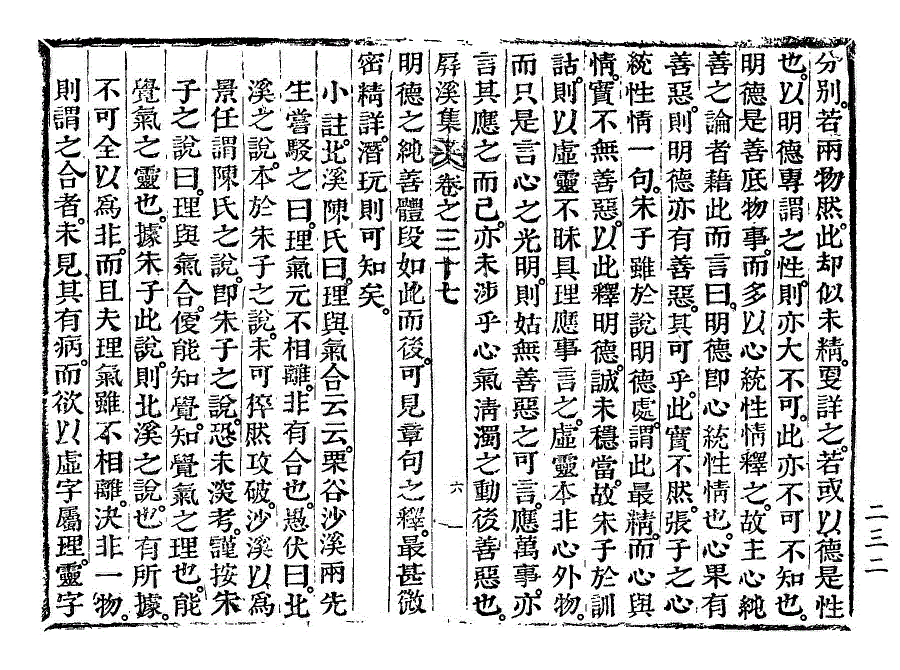 分别。若两物然。此却似未精。更详之。若或以德是性也。以明德专谓之性。则亦大不可。此亦不可不知也。明德是善底物事。而多以心统性情释之。故主心纯善之论者藉此而言曰。明德即心统性情也。心果有善恶。则明德亦有善恶。其可乎。此实不然。张子之心统性情一句。朱子虽于说明德处。谓此最精。而心与情。实不无善恶。以此释明德。诚未稳当。故朱子于训诂。则以虚灵不昧具理应事言之。虚灵本非心外物。而只是言心之光明。则姑无善恶之可言。应万事。亦言其应之而已。亦未涉乎心气清浊之动后善恶也。明德之纯善体段如此而后。可见章句之释。最甚微密精详。潜玩则可知矣。
分别。若两物然。此却似未精。更详之。若或以德是性也。以明德专谓之性。则亦大不可。此亦不可不知也。明德是善底物事。而多以心统性情释之。故主心纯善之论者藉此而言曰。明德即心统性情也。心果有善恶。则明德亦有善恶。其可乎。此实不然。张子之心统性情一句。朱子虽于说明德处。谓此最精。而心与情。实不无善恶。以此释明德。诚未稳当。故朱子于训诂。则以虚灵不昧具理应事言之。虚灵本非心外物。而只是言心之光明。则姑无善恶之可言。应万事。亦言其应之而已。亦未涉乎心气清浊之动后善恶也。明德之纯善体段如此而后。可见章句之释。最甚微密精详。潜玩则可知矣。小注。北溪陈氏曰。理与气合云云。栗谷沙溪两先生尝驳之曰。理气元不相离。非有合也。愚伏曰。北溪之说。本于朱子之说。未可猝然攻破。沙溪以为景任谓陈氏之说。即朱子之说。恐未深考。谨按朱子之说曰。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知觉气之理也。能觉气之灵也。据朱子此说。则北溪之说。也有所据。不可全以为非。而且夫理气虽不相离。决非一物。则谓之合者。未见其有病。而欲以虚字属理。灵字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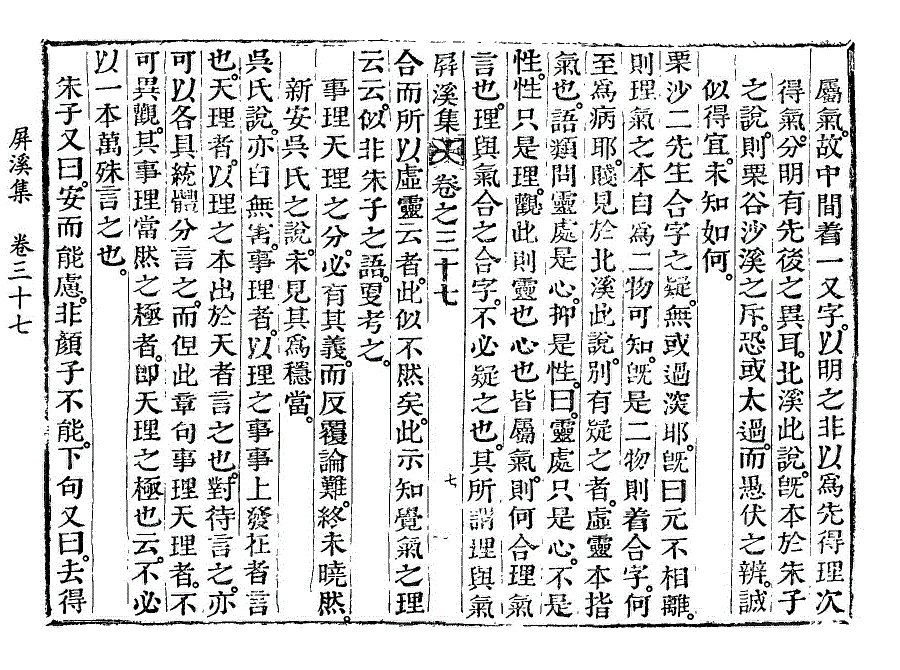 属气。故中间着一又字。以明之非以为先得理次得气。分明有先后之异耳。北溪此说。既本于朱子之说。则栗谷沙溪之斥。恐或太过。而愚伏之辨。诚似得宜。未知如何。
属气。故中间着一又字。以明之非以为先得理次得气。分明有先后之异耳。北溪此说。既本于朱子之说。则栗谷沙溪之斥。恐或太过。而愚伏之辨。诚似得宜。未知如何。栗沙二先生合字之疑。无或过深耶。既曰元不相离。则理气之本自为二物可知。既是二物则着合字。何至为病耶。贱见于北溪此说。别有疑之者。虚灵本指气也。语类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观此则灵也心也皆属气。则何合理气言也。理与气合之合字。不必疑之也。其所谓理与气合而所以虚灵云者。此似不然矣。此示知觉气之理云云。似非朱子之语。更考之。
事理天理之分。必有其义。而反覆论难。终未晓然。新安吴氏之说。未见其为稳当。
吴氏说。亦自无害。事理者。以理之事事上发在者言也。天理者。以理之本出于天者言之也。对待言之。亦可以各具统体分言之。而但此章句事理天理者。不可异观。其事理当然之极者。即天理之极也云。不必以一本万殊言之也。
朱子又曰。安而能虑。非颜子不能。下句又曰。去得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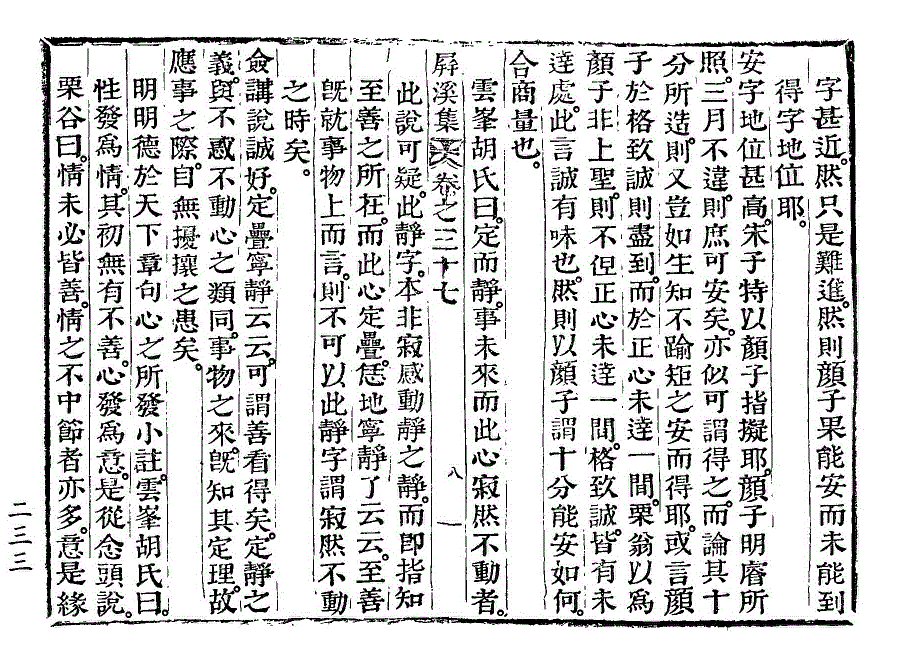 字甚近。然只是难进。然则颜子果能安而未能到得字地位耶。
字甚近。然只是难进。然则颜子果能安而未能到得字地位耶。安字地位甚高。朱子特以颜子指拟耶。颜子明睿所照。三月不违。则庶可安矣。亦似可谓得之。而论其十分所造。则又岂如生知不踰矩之安而得耶。或言颜子于格致诚则尽到。而于正心未达一间。栗翁以为颜子非上圣。则不但正心未达一间。格致诚。皆有未达处。此言诚有味也。然则以颜子谓十分能安如何。合商量也。
云峰胡氏曰。定而静。事未来而此心寂然不动者。此说可疑。此静字。本非寂感动静之静。而即指知至善之所在。而此心定叠。恁地宁静了云云。至善既就事物上而言。则不可以此静字谓寂然不动之时矣。
佥讲说诚好。定叠宁静云云。可谓善看得矣。定静之义。与不惑不动心之类同。事物之来。既知其定理。故应事之际。自无扰攘之患矣。
明明德于天下章句心之所发小注。云峰胡氏曰。性发为情。其初无有不善。心发为意。是从念头说。栗谷曰。情未必皆善。情之不中节者亦多。意是缘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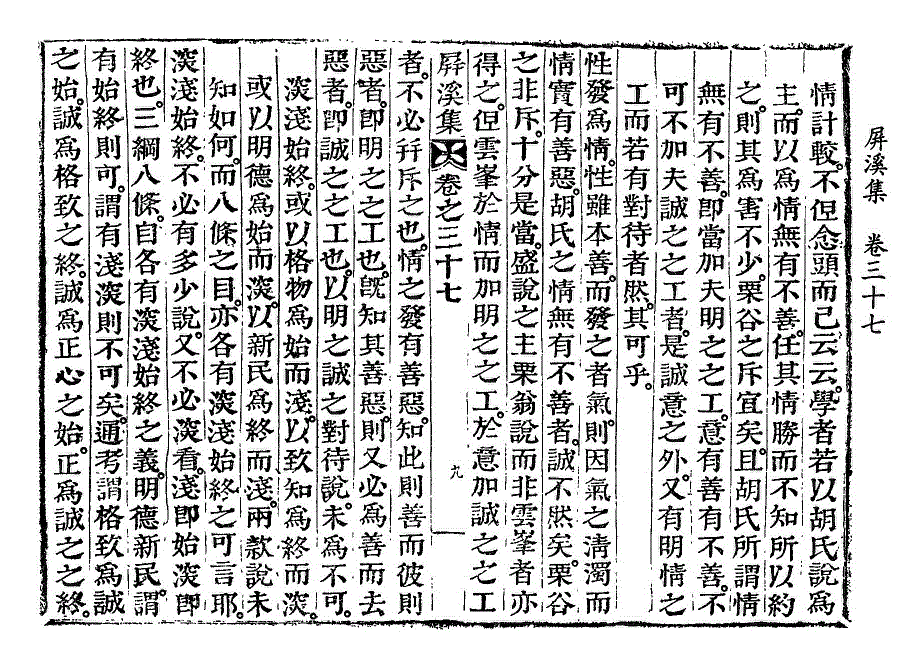 情计较。不但念头而已云云。学者若以胡氏说为主。而以为情无有不善。任其情胜而不知所以约之。则其为害不少。栗谷之斥宜矣。且胡氏所谓情无有不善。即当加夫明之之工。意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工者。是诚意之外。又有明情之工而若有对待者然。其可乎。
情计较。不但念头而已云云。学者若以胡氏说为主。而以为情无有不善。任其情胜而不知所以约之。则其为害不少。栗谷之斥宜矣。且胡氏所谓情无有不善。即当加夫明之之工。意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工者。是诚意之外。又有明情之工而若有对待者然。其可乎。性发为情。性虽本善。而发之者气。则因气之清浊而情实有善恶。胡氏之情无有不善者。诚不然矣。栗谷之非斥。十分是当。盛说之主栗翁说而非云峰者亦得之。但云峰于情而加明之之工。于意加诚之之工者。不必并斥之也。情之发有善恶。知此则善而彼则恶者。即明之之工也。既知其善恶。则又必为善而去恶者。即诚之之工也。以明之诚之对待说。未为不可。
深浅始终。或以格物为始而浅。以致知为终而深。或以明德为始而深。以新民为终而浅。两款说未知如何。而八条之目。亦各有深浅始终之可言耶。
深浅始终。不必有多少说。又不必深看。浅即始深即终也。三纲八条。自各有深浅始终之义。明德新民。谓有始终则可。谓有浅深则不可矣。通考谓格致为诚之始。诚为格致之终。诚为正心之始。正为诚之之终。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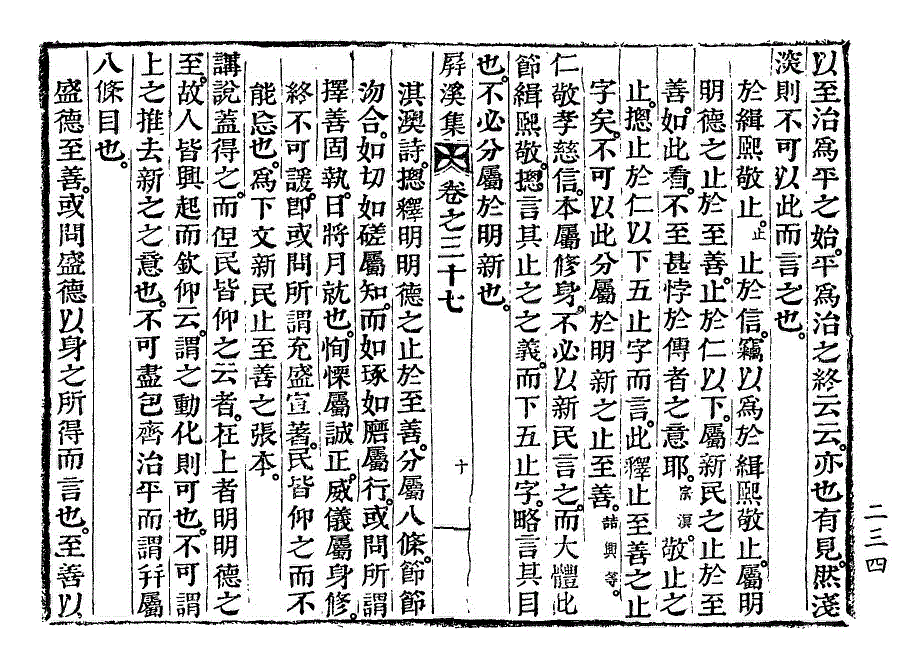 以至治为平之始。平为治之终云云。亦也有见。然浅深则不可以此而言之也。
以至治为平之始。平为治之终云云。亦也有见。然浅深则不可以此而言之也。于缉熙敬止。(止)止于信。窃以为于缉熙敬止。属明明德之止于至善。止于仁以下。属新民之止于至善。如此看。不至甚悖于传者之意耶。(宗溟。)敬止之止。总止于仁以下五止字而言。此释止至善之止字矣。不可以此分属于明新之止至善。(哲兴等。)
仁敬孝慈信。本属修身。不必以新民言之。而大体此节缉熙敬。总言其止之之义。而下五止字。略言其目也。不必分属于明新也。
淇澳诗。总释明明德之止于至善。分属八条。节节沕合。如切如磋属知。而如琢如磨属行。或问所谓择善固执。日将月就也。恂慄属诚正。威仪属身修。终不可谖。即或问所谓充盛宣著。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为下文新民止至善之张本。
讲说盖得之。而但民皆仰之云者。在上者明明德之至。故人皆兴起而钦仰云。谓之动化则可也。不可谓上之推去新之之意也。不可尽包齐治平而谓并属八条目也。
盛德至善。或问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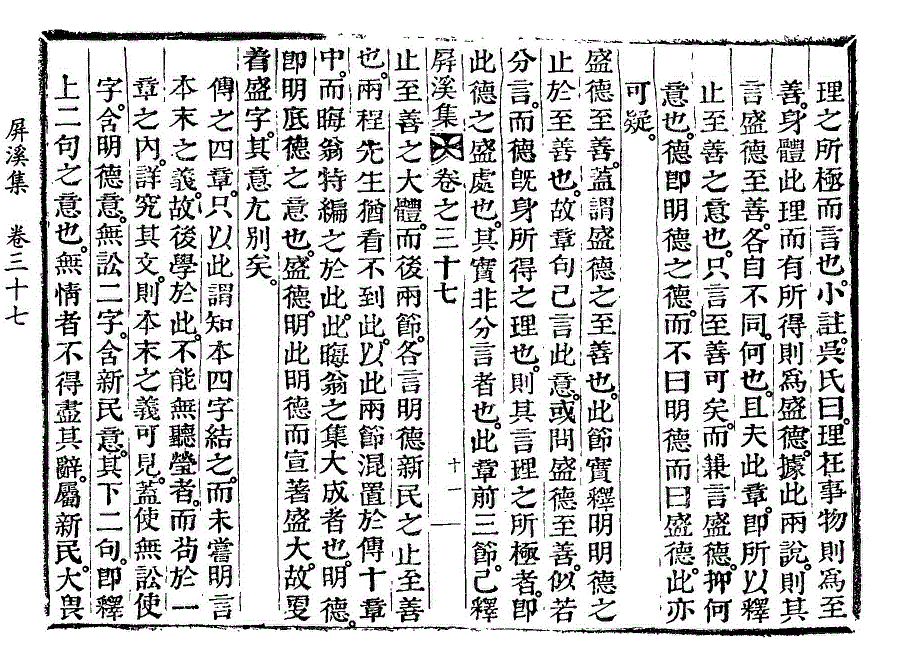 理之所极而言也。小注。吴氏曰。理在事物则为至善。身体此理而有所得则为盛德。据此两说。则其言盛德至善。各自不同。何也。且夫此章。即所以释止至善之意也。只言至善可矣。而兼言盛德。抑何意也。德即明德之德。而不曰明德而曰盛德。此亦可疑。
理之所极而言也。小注。吴氏曰。理在事物则为至善。身体此理而有所得则为盛德。据此两说。则其言盛德至善。各自不同。何也。且夫此章。即所以释止至善之意也。只言至善可矣。而兼言盛德。抑何意也。德即明德之德。而不曰明德而曰盛德。此亦可疑。盛德至善。盖谓盛德之至善也。此节实释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也。故章句已言此意。或问盛德至善。似若分言。而德既身所得之理也。则其言理之所极者。即此德之盛处也。其实非分言者也。此章前三节。已释止至善之大体。而后两节。各言明德新民之止至善也。两程先生犹看不到此。以此两节混置于传十章中。而晦翁特编之于此。此晦翁之集大成者也。明德。即明底德之意也。盛德。明此明德而宣著盛大。故更着盛字。其意尤别矣。
传之四章。只以此谓知本四字结之。而未尝明言本末之义。故后学于此。不能无听莹者。而苟于一章之内。详究其文。则本末之义可见。盖使无讼使字。含明德意。无讼二字。含新民意。其下二句。即释上二句之意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属新民。大畏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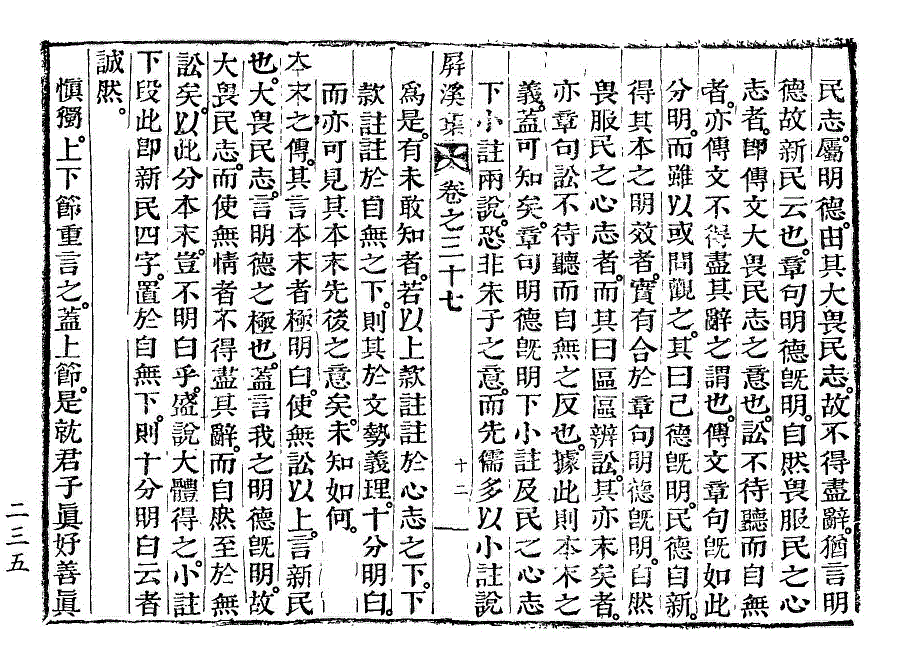 民志。属明德。由其大畏民志。故不得尽辞。犹言明德故新民云也。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即传文大畏民志之意也。讼不待听而自无者。亦传文不得尽其辞之谓也。传文章句既如此分明。而虽以或问观之。其曰己德既明。民德自新。得其本之明效者。实有合于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而其曰区区辨讼。其亦末矣者。亦章句讼不待听而自无之反也。据此则本末之义。盖可知矣。章句明德既明下小注及民之心志下小注两说。恐非朱子之意。而先儒多以小注说为是。有未敢知者。若以上款注注于心志之下。下款注注于自无之下。则其于文势义理。十分明白。而亦可见其本末先后之意矣。未知如何。
民志。属明德。由其大畏民志。故不得尽辞。犹言明德故新民云也。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即传文大畏民志之意也。讼不待听而自无者。亦传文不得尽其辞之谓也。传文章句既如此分明。而虽以或问观之。其曰己德既明。民德自新。得其本之明效者。实有合于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而其曰区区辨讼。其亦末矣者。亦章句讼不待听而自无之反也。据此则本末之义。盖可知矣。章句明德既明下小注及民之心志下小注两说。恐非朱子之意。而先儒多以小注说为是。有未敢知者。若以上款注注于心志之下。下款注注于自无之下。则其于文势义理。十分明白。而亦可见其本末先后之意矣。未知如何。本末之传。其言本末者极明白。使无讼以上。言新民也。大畏民志。言明德之极也。盖言我之明德既明。故大畏民志。而使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而自然至于无讼矣。以此分本末。岂不明白乎。盛说大体得之。小注下段此即新民四字。置于自无下。则十分明白云者诚然。
慎独。上下节重言之。盖上节。是就君子真好善真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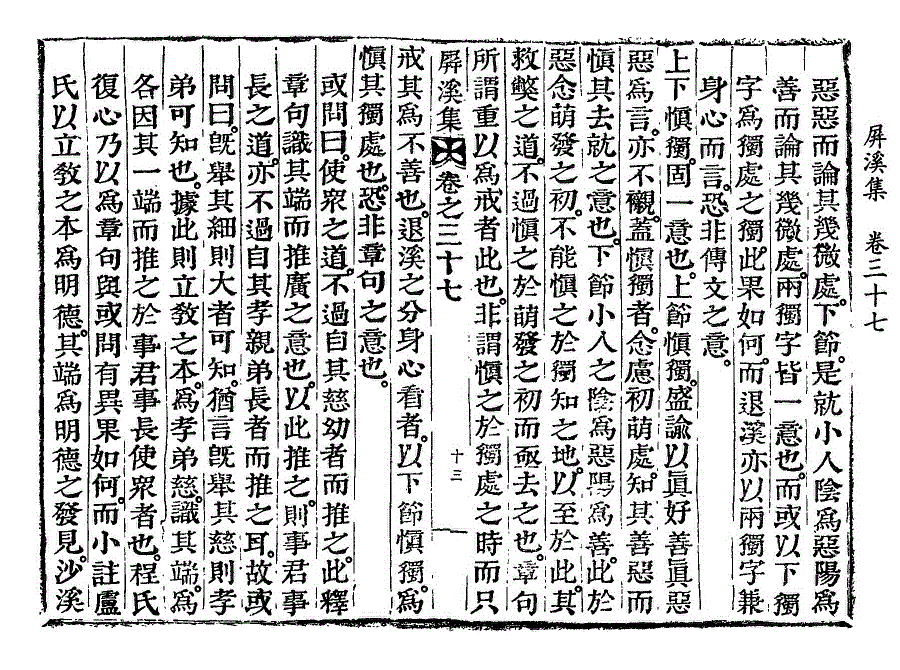 恶恶而论其几微处。下节。是就小人阴为恶阳为善而论其几微处。两独字皆一意也。而或以下独字为独处之独。此果如何。而退溪亦以两独字兼身心而言。恐非传文之意。
恶恶而论其几微处。下节。是就小人阴为恶阳为善而论其几微处。两独字皆一意也。而或以下独字为独处之独。此果如何。而退溪亦以两独字兼身心而言。恐非传文之意。上下慎独。固一意也。上节慎独。盛谕以真好善真恶恶为言。亦不衬。盖慎独者。念虑初萌处。知其善恶而慎其去就之意也。下节小人之阴为恶阳为善。此于恶念萌发之初。不能慎之于独知之地。以至于此。其救弊之道。不过慎之于萌发之初而亟去之也。章句所谓重以为戒者此也。非谓慎之于独处之时而只戒其为不善也。退溪之分身心看者。以下节慎独。为慎其独处也。恐非章句之意也。
或问曰。使众之道。不过自其慈幼者而推之。此释章句识其端而推广之意也。以此推之。则事君事长之道。亦不过自其孝亲弟长者而推之耳。故或问曰。既举其细则大者可知。犹言既举其慈则孝弟可知也。据此则立教之本。为孝弟慈。识其端。为各因其一端而推之于事君事长使众者也。程氏复心乃以为章句与或问有异果如何。而小注卢氏以立教之本为明德。其端为明德之发见。沙溪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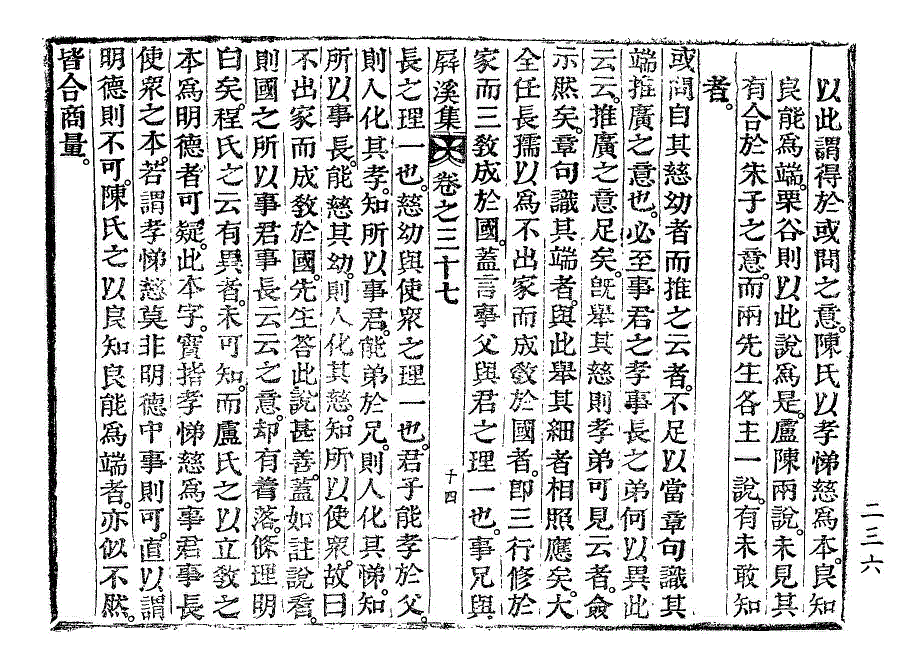 以此谓得于或问之意。陈氏以孝悌慈为本。良知良能为端。栗谷则以此说为是。卢陈两说。未见其有合于朱子之意。而两先生各主一说。有未敢知者。
以此谓得于或问之意。陈氏以孝悌慈为本。良知良能为端。栗谷则以此说为是。卢陈两说。未见其有合于朱子之意。而两先生各主一说。有未敢知者。或问自其慈幼者而推之云者。不足以当章句识其端推广之意也。必至事君之孝事长之弟何以异此云云。推广之意足矣。既举其慈则孝弟可见云者。佥示然矣。章句识其端者。与此举其细者相照应矣。大全任长孺以为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即三行修于家而三教成于国。盖言事父与君之理一也。事兄与长之理一也。慈幼与使众之理一也。君子能孝于父。则人化其孝。知所以事君。能弟于兄。则人化其悌。知所以事长。能慈其幼。则人化其慈。知所以使众。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先生答此说甚善。盖如注说看。则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云云之意。却有着落。条理明白矣。程氏之云有异者。未可知。而卢氏之以立教之本为明德者可疑。此本字。实指孝悌慈为事君事长使众之本。若谓孝悌慈莫非明德中事则可。直以谓明德则不可。陈氏之以良知良能为端者。亦似不然。皆合商量。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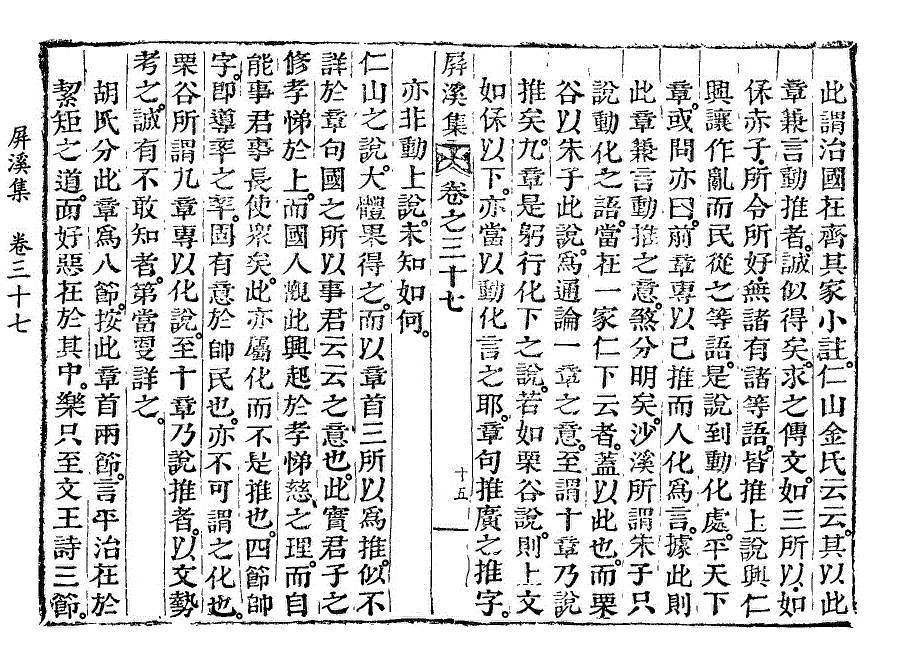 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小注。仁山金氏云云。其以此章兼言动推者。诚似得矣。求之传文。如三所以,如保赤子,所令所好,无诸有诸等语。皆推上说兴仁兴让作乱而民从之等语。是说到动化处。平天下章。或问亦曰。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据此则此章兼言动推之意。煞分明矣。沙溪所谓朱子只说动化之语。当在一家仁下云者。盖以此也。而栗谷以朱子此说。为通论一章之意。至谓十章乃说推矣。九章是躬行化下之说。若如栗谷说。则上文如保以下。亦当以动化言之耶。章句推广之推字。亦非动上说。未知如何。
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小注。仁山金氏云云。其以此章兼言动推者。诚似得矣。求之传文。如三所以,如保赤子,所令所好,无诸有诸等语。皆推上说兴仁兴让作乱而民从之等语。是说到动化处。平天下章。或问亦曰。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据此则此章兼言动推之意。煞分明矣。沙溪所谓朱子只说动化之语。当在一家仁下云者。盖以此也。而栗谷以朱子此说。为通论一章之意。至谓十章乃说推矣。九章是躬行化下之说。若如栗谷说。则上文如保以下。亦当以动化言之耶。章句推广之推字。亦非动上说。未知如何。仁山之说。大体果得之。而以章首三所以为推。似不详于章句国之所以事君云云之意也。此实君子之修孝悌于上。而国人观此兴起于孝悌慈之理。而自能事君事长使众矣。此亦属化而不是推也。四节帅字。即导率之率。固有意于帅民也。亦不可谓之化也。栗谷所谓九章专以化说。至十章乃说推者。以文势考之。诚有不敢知者。第当更详之。
胡氏分此章为八节。按此章首两节。言平治在于絜矩之道。而好恶在于其中。乐只至文王诗三节。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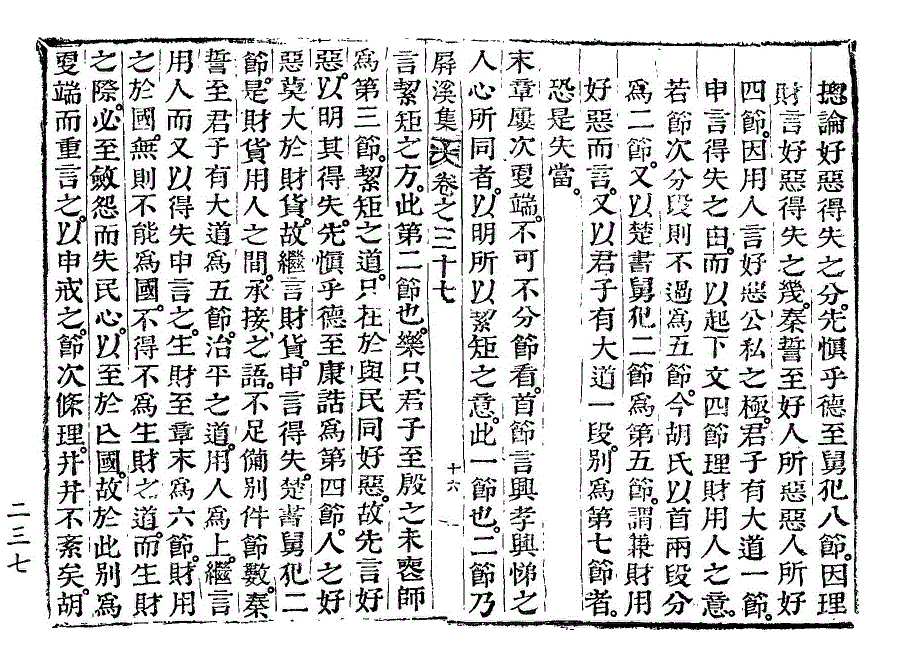 总论好恶得失之分。先慎乎德至舅犯八节。因理财言好恶得失之几。秦誓至好人所恶恶人所好四节。因用人言好恶公私之极。君子有大道一节。申言得失之由。而以起下文四节理财用人之意。若节次分段则不过为五节。今胡氏以首两段分为二节。又以楚书舅犯二节为第五节。谓兼财用好恶而言。又以君子有大道一段。别为第七节者。恐是失当。
总论好恶得失之分。先慎乎德至舅犯八节。因理财言好恶得失之几。秦誓至好人所恶恶人所好四节。因用人言好恶公私之极。君子有大道一节。申言得失之由。而以起下文四节理财用人之意。若节次分段则不过为五节。今胡氏以首两段分为二节。又以楚书舅犯二节为第五节。谓兼财用好恶而言。又以君子有大道一段。别为第七节者。恐是失当。末章屡次更端。不可不分节看。首节言兴孝兴悌之人心所同者。以明所以絜矩之意。此一节也。二节乃言絜矩之方。此第二节也。乐只君子至殷之未丧师为第三节。絜矩之道。只在于与民同好恶。故先言好恶。以明其得失。先慎乎德至康诰为第四节。人之好恶莫大于财货。故继言财货。申言得失。楚书舅犯二节。是财货用人之间。承接之语。不足备别件节数。秦誓至君子有大道为五节。治平之道。用人为上。继言用人而又以得失申言之。生财至章末为六节。财用之于国。无则不能为国。不得不为生财之道。而生财之际。必至敛怨而失民心。以至于亡国。故于此别为更端而重言之。以申戒之。节次条理。井井不紊矣。胡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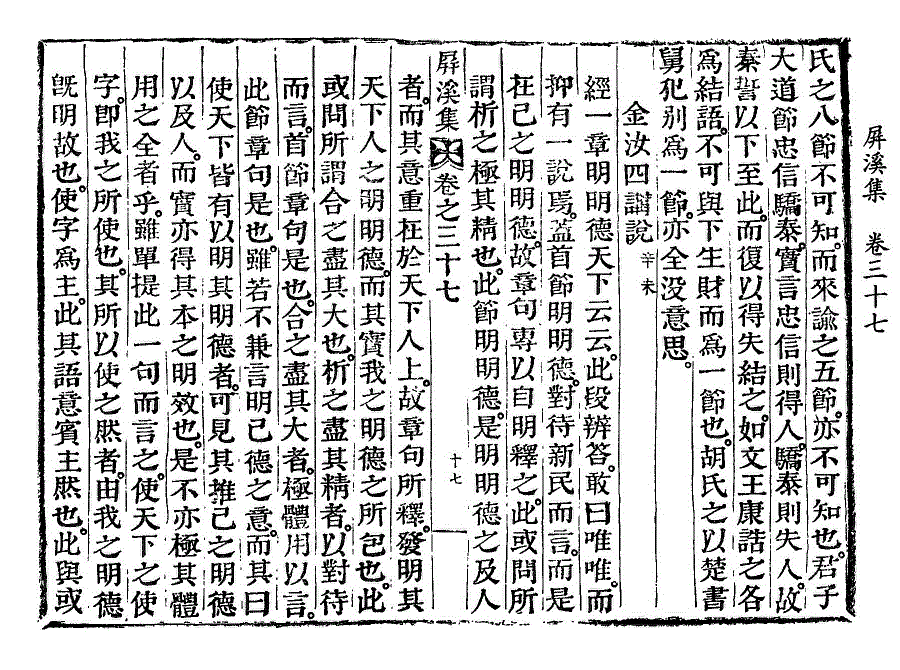 氏之八节不可知。而来谕之五节。亦不可知也。君子大道节忠信骄泰。实言忠信则得人。骄泰则失人。故秦誓以下至此。而复以得失结之。如文王康诰之各为结语。不可与下生财而为一节也。胡氏之以楚书舅犯别为一节。亦全没意思。
氏之八节不可知。而来谕之五节。亦不可知也。君子大道节忠信骄泰。实言忠信则得人。骄泰则失人。故秦誓以下至此。而复以得失结之。如文王康诰之各为结语。不可与下生财而为一节也。胡氏之以楚书舅犯别为一节。亦全没意思。金汝四讲说(辛未)
经一章明明德天下云云。此段辨答。敢曰唯唯。而抑有一说焉。盖首节明明德。对待新民而言。而是在己之明明德。故章句专以自明释之。此或问所谓析之极其精也。此节明明德。是明明德之及人者。而其意重在于天下人上。故章句所释。发明其天下人之明明德。而其实我之明德之所包也。此或问所谓合之尽其大也。析之尽其精者。以对待而言。首节章句是也。合之尽其大者。极体用以言。此节章句是也。虽若不兼言明己德之意。而其曰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者。可见其推己之明德以及人。而实亦得其本之明效也。是不亦极其体用之全者乎。虽单提此一句而言之。使天下之使字。即我之所使也。其所以使之然者。由我之明德既明故也。使字为主。此其语意宾主然也。此与或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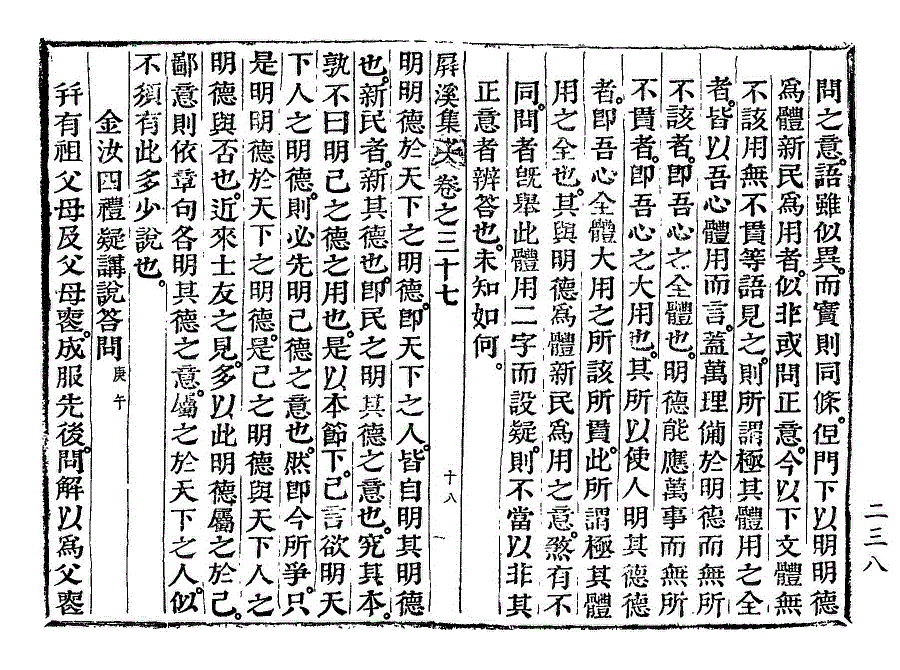 问之意。语虽似异。而实则同条。但门下以明明德为体新民为用者。似非或问正意。今以下文体无不该用无不贯等语见之。则所谓极其体用之全者。皆以吾心体用而言。盖万理备于明德而无所不该者。即吾心之全体也。明德能应万事而无所不贯者。即吾心之大用也。其所以使人明其德德者。即吾心全体大用之所该所贯。此所谓极其体用之全也。其与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之意。煞有不同。问者既举此体用二字而设疑。则不当以非其正意者辨答也。未知如何。
问之意。语虽似异。而实则同条。但门下以明明德为体新民为用者。似非或问正意。今以下文体无不该用无不贯等语见之。则所谓极其体用之全者。皆以吾心体用而言。盖万理备于明德而无所不该者。即吾心之全体也。明德能应万事而无所不贯者。即吾心之大用也。其所以使人明其德德者。即吾心全体大用之所该所贯。此所谓极其体用之全也。其与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之意。煞有不同。问者既举此体用二字而设疑。则不当以非其正意者辨答也。未知如何。明明德于天下之明德。即天下之人。皆自明其明德也。新民者。新其德也。即民之明其德之意也。究其本。孰不曰明己之德之用也。是以本节下。已言欲明天下人之明德。则必先明己德之意也。然即今所争。只是明明德于天下之明德。是己之明德与天下人之明德与否也。近来士友之见。多以此明德属之于己。鄙意则依章句各明其德之意。属之于天下之人。似不须有此多少说也。
金汝四礼疑讲说答问(庚午)
并有祖父母及父母丧。成服先后。问解以为父丧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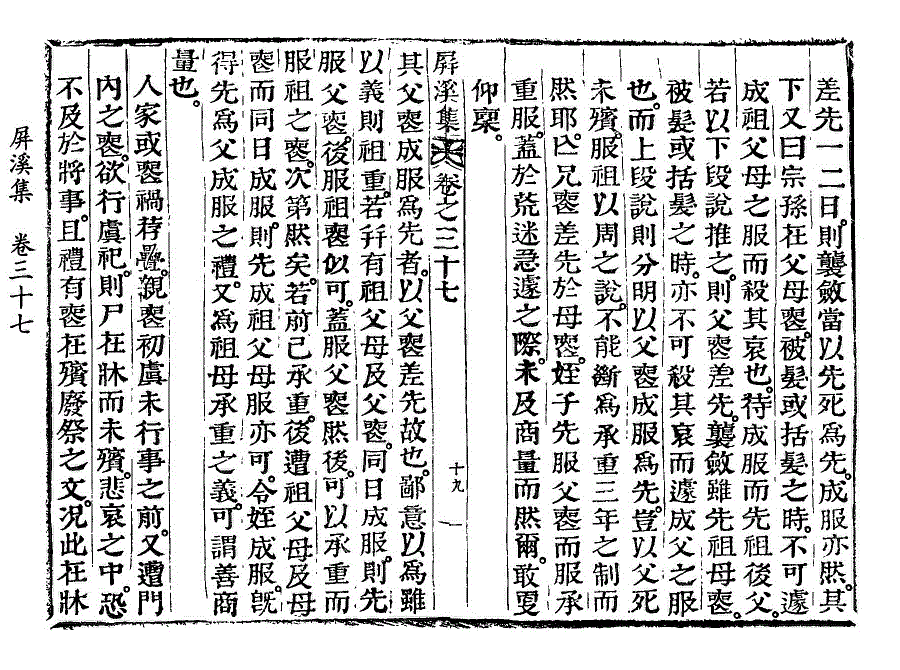 差先一二日。则袭敛当以先死为先。成服亦然。其下又曰宗孙在父母丧。被发或括发之时。不可遽成祖父母之服而杀其哀也。待成服而先祖后父。若以下段说推之。则父丧差先。袭敛虽先祖母丧。被发或括发之时。亦不可杀其哀而遽成父之服也。而上段说则分明以父丧成服为先。岂以父死未殡。服祖以周之说。不能断为承重三年之制而然耶。亡兄丧差先于母丧。侄子先服父丧而服承重服。盖于荒迷急遽之际。未及商量而然尔。敢更仰禀。
差先一二日。则袭敛当以先死为先。成服亦然。其下又曰宗孙在父母丧。被发或括发之时。不可遽成祖父母之服而杀其哀也。待成服而先祖后父。若以下段说推之。则父丧差先。袭敛虽先祖母丧。被发或括发之时。亦不可杀其哀而遽成父之服也。而上段说则分明以父丧成服为先。岂以父死未殡。服祖以周之说。不能断为承重三年之制而然耶。亡兄丧差先于母丧。侄子先服父丧而服承重服。盖于荒迷急遽之际。未及商量而然尔。敢更仰禀。其父丧成服为先者。以父丧差先故也。鄙意以为虽以义则祖重。若并有祖父母及父丧。同日成服。则先服父丧。后服祖丧似可。盖服父丧然后。可以承重而服祖之丧。次第然矣。若前已承重。后遭祖父母及母丧而同日成服。则先成祖父母服亦可。令侄成服。既得先为父成服之礼。又为祖母承重之义。可谓善商量也。
人家或丧祸荐叠。亲丧初虞未行事之前。又遭门内之丧。欲行虞祀。则尸在床而未殡。悲哀之中。恐不及于将事。且礼有丧在殡废祭之文。况此在床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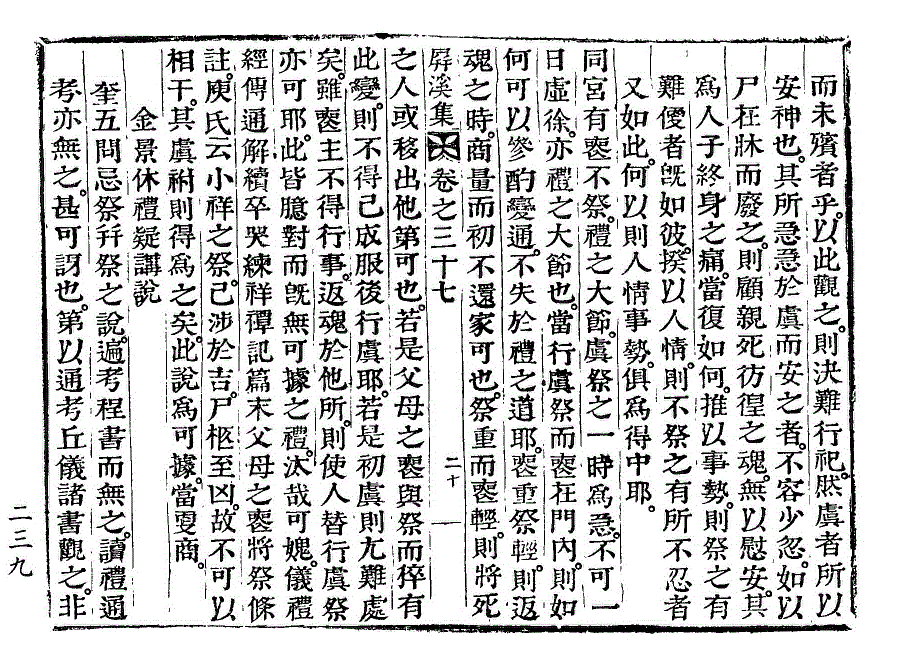 而未殡者乎。以此观之。则决难行祀。然虞者所以安神也。其所急急于虞而安之者。不容少忽。如以尸在床而废之。则顾亲死彷徨之魂。无以慰安。其为人子终身之痛。当复如何。推以事势。则祭之有难便者既如彼。揆以人情。则不祭之有所不忍者又如此。何以则人情事势。俱为得中耶。
而未殡者乎。以此观之。则决难行祀。然虞者所以安神也。其所急急于虞而安之者。不容少忽。如以尸在床而废之。则顾亲死彷徨之魂。无以慰安。其为人子终身之痛。当复如何。推以事势。则祭之有难便者既如彼。揆以人情。则不祭之有所不忍者又如此。何以则人情事势。俱为得中耶。同宫有丧不祭。礼之大节。虞祭之一时为急。不可一日虚徐。亦礼之大节也。当行虞祭而丧在门内。则如何可以参酌变通。不失于礼之道耶。丧重祭轻。则返魂之时。商量而初不还家可也。祭重而丧轻。则将死之人或移出他第可也。若是父母之丧与祭而猝有此变。则不得已成服后行虞耶。若是初虞则尤难处矣。虽丧主不得行事。返魂于他所。则使人替行虞祭亦可耶。此皆臆对而既无可据之礼。汰哉可愧。仪礼经传通解续卒哭练祥禫记篇末父母之丧将祭条注。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则得为之矣。此说为可据。当更商。
金景休礼疑讲说
奎五问忌祭并祭之说。遍考程书而无之。读礼通考亦无之。甚可讶也。第以通考丘仪诸书观之。非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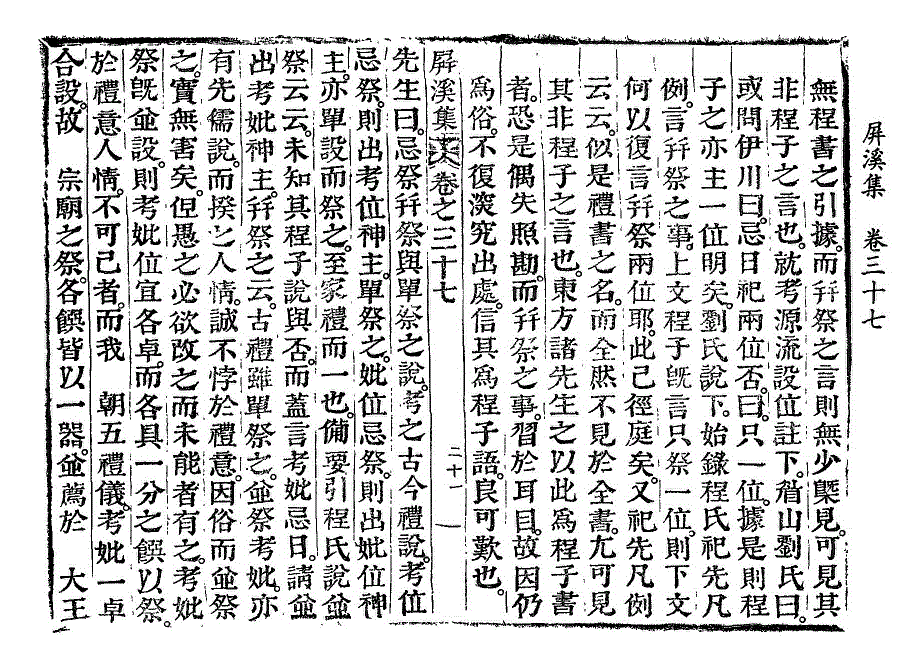 无程书之引据。而并祭之言则无少槩见。可见其非程子之言也。就考源流设位注下。眉山刘氏曰。或问伊川曰。忌日祀两位否。曰。只一位。据是则程子之亦主一位明矣。刘氏说下。始录程氏祀先凡例。言并祭之事。上文程子既言只祭一位。则下文何以复言并祭两位耶。此已径庭矣。又祀先凡例云云。似是礼书之名。而全然不见于全书。尤可见其非程子之言也。东方诸先生之以此为程子书者。恐是偶失照勘。而并祭之事。习于耳目。故因仍为俗。不复深究出处。信其为程子语。良可叹也。
无程书之引据。而并祭之言则无少槩见。可见其非程子之言也。就考源流设位注下。眉山刘氏曰。或问伊川曰。忌日祀两位否。曰。只一位。据是则程子之亦主一位明矣。刘氏说下。始录程氏祀先凡例。言并祭之事。上文程子既言只祭一位。则下文何以复言并祭两位耶。此已径庭矣。又祀先凡例云云。似是礼书之名。而全然不见于全书。尤可见其非程子之言也。东方诸先生之以此为程子书者。恐是偶失照勘。而并祭之事。习于耳目。故因仍为俗。不复深究出处。信其为程子语。良可叹也。先生曰。忌祭并祭与单祭之说。考之古今礼说。考位忌祭。则出考位神主。单祭之。妣位忌祭。则出妣位神主。亦单设而祭之。至家礼而一也。备要引程氏说并祭云云。未知其程子说与否。而盖言考妣忌日。请并出考妣神主。并祭之云。古礼虽单祭之。并祭考妣。亦有先儒说。而揆之人情。诚不悖于礼意。因俗而并祭之。实无害矣。但愚之必欲改之而未能者有之。考妣祭既并设。则考妣位宜各卓。而各具一分之馔以祭。于礼意人情。不可已者。而我 朝五礼仪。考妣一卓合设。故 宗庙之祭。各馔皆以一器。并荐于 大王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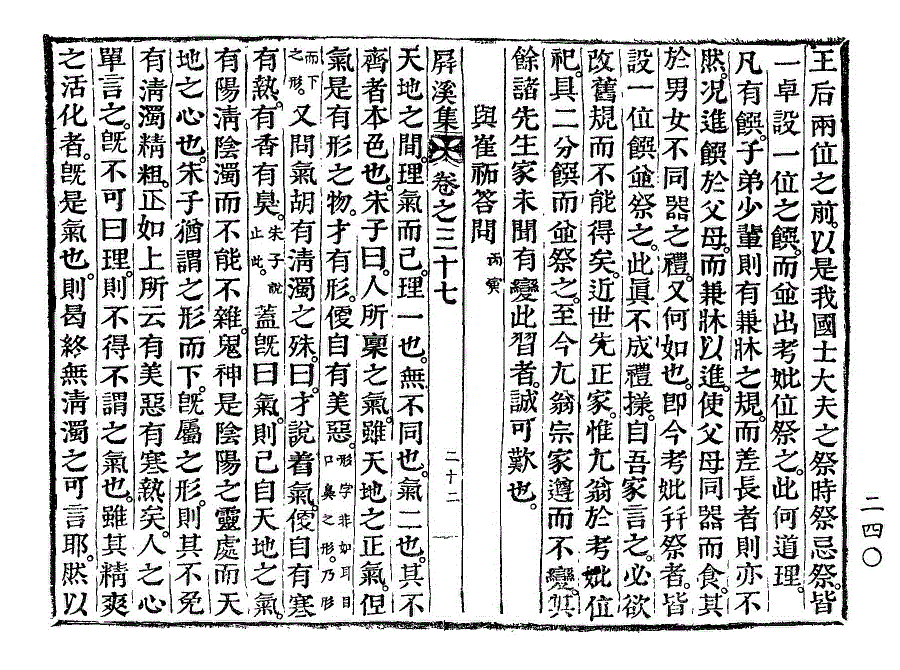 王后两位之前。以是我国士大夫之祭时祭忌祭。皆一卓设一位之馔。而并出考妣位祭之。此何道理。
王后两位之前。以是我国士大夫之祭时祭忌祭。皆一卓设一位之馔。而并出考妣位祭之。此何道理。凡有馔。子弟少辈则有兼床之规。而差长者则亦不然。况进馔于父母。而兼床以进。使父母同器而食。其于男女不同器之礼。又何如也。即今考妣并祭者。皆设一位馔并祭之。此真不成礼㨾。自吾家言之。必欲改旧规而不能得矣。近世先正家。惟尤翁于考妣位祀。具二分馔而并祭之。至今尤翁宗家遵而不变。其馀诸先生家未闻有变此习者。诚可叹也。
与崔祏答问(丙寅)
天地之间。理气而已。理一也。无不同也。气二也。其不齐者本色也。朱子曰。人所禀之气。虽天地之正气。但气是有形之物。才有形。便自有美恶。(形字非如耳目口鼻之形。乃形而下之形。)又问气胡有清浊之殊。曰。才说着气。便自有寒有热。有香有臭。(朱子说止此。)盖既曰气。则已自天地之气。有阳清阴浊而不能不杂。鬼神是阴阳之灵处而天地之心也。朱子犹谓之形而下。既属之形。则其不免有清浊精粗。正如上所云有美恶有寒热矣。人之心单言之。既不可曰理。则不得不谓之气也。虽其精爽之活化者。既是气也。则曷终无清浊之可言耶。然以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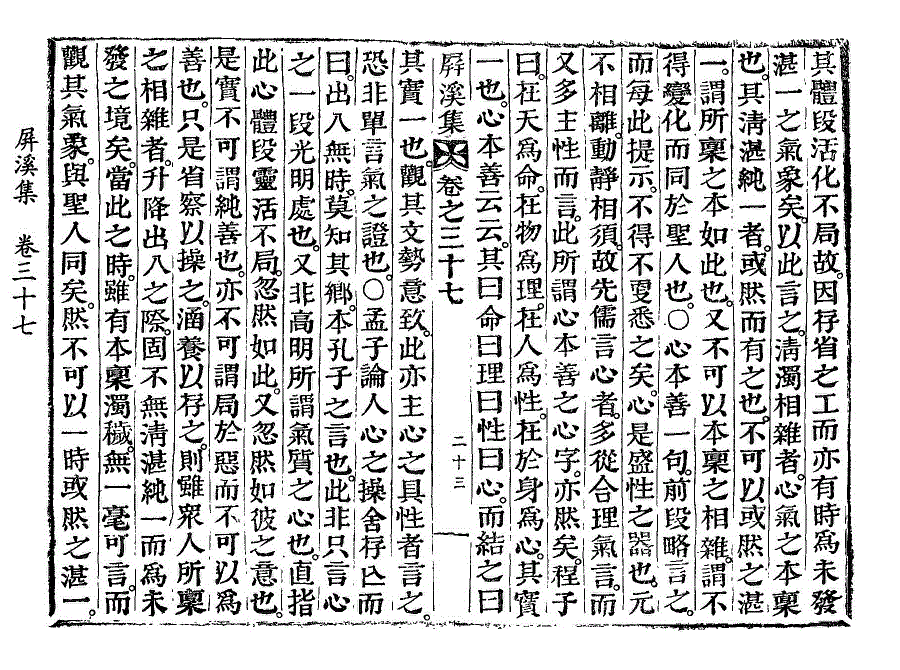 其体段活化不局故。因存省之工而亦有时为未发湛一之气象矣。以此言之。清浊相杂者。心气之本禀也。其清湛纯一者。或然而有之也。不可以或然之湛一。谓所禀之本如此也。又不可以本禀之相杂。谓不得变化而同于圣人也。○心本善一句。前段略言之。而每此提示。不得不更悉之矣。心是盛性之器也。元不相离。动静相须。故先儒言心者。多从合理气言。而又多主性而言。此所谓心本善之心字。亦然矣。程子曰。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在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云云。其曰命曰理曰性曰心。而结之曰其实一也。观其文势意致。此亦主心之具性者言之。恐非单言气之證也。○孟子论人心之操舍存亡而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本孔子之言也。此非只言心之一段光明处也。又非高明所谓气质之心也。直指此心体段灵活不局。忽然如此。又忽然如彼之意也。是实不可谓纯善也。亦不可谓局于恶而不可以为善也。只是省察以操之。涵养以存之。则虽众人所禀之相杂者。升降出入之际。固不无清湛纯一而为未发之境矣。当此之时。虽有本禀浊秽。无一毫可言。而观其气象。与圣人同矣。然不可以一时或然之湛一。
其体段活化不局故。因存省之工而亦有时为未发湛一之气象矣。以此言之。清浊相杂者。心气之本禀也。其清湛纯一者。或然而有之也。不可以或然之湛一。谓所禀之本如此也。又不可以本禀之相杂。谓不得变化而同于圣人也。○心本善一句。前段略言之。而每此提示。不得不更悉之矣。心是盛性之器也。元不相离。动静相须。故先儒言心者。多从合理气言。而又多主性而言。此所谓心本善之心字。亦然矣。程子曰。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在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云云。其曰命曰理曰性曰心。而结之曰其实一也。观其文势意致。此亦主心之具性者言之。恐非单言气之證也。○孟子论人心之操舍存亡而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本孔子之言也。此非只言心之一段光明处也。又非高明所谓气质之心也。直指此心体段灵活不局。忽然如此。又忽然如彼之意也。是实不可谓纯善也。亦不可谓局于恶而不可以为善也。只是省察以操之。涵养以存之。则虽众人所禀之相杂者。升降出入之际。固不无清湛纯一而为未发之境矣。当此之时。虽有本禀浊秽。无一毫可言。而观其气象。与圣人同矣。然不可以一时或然之湛一。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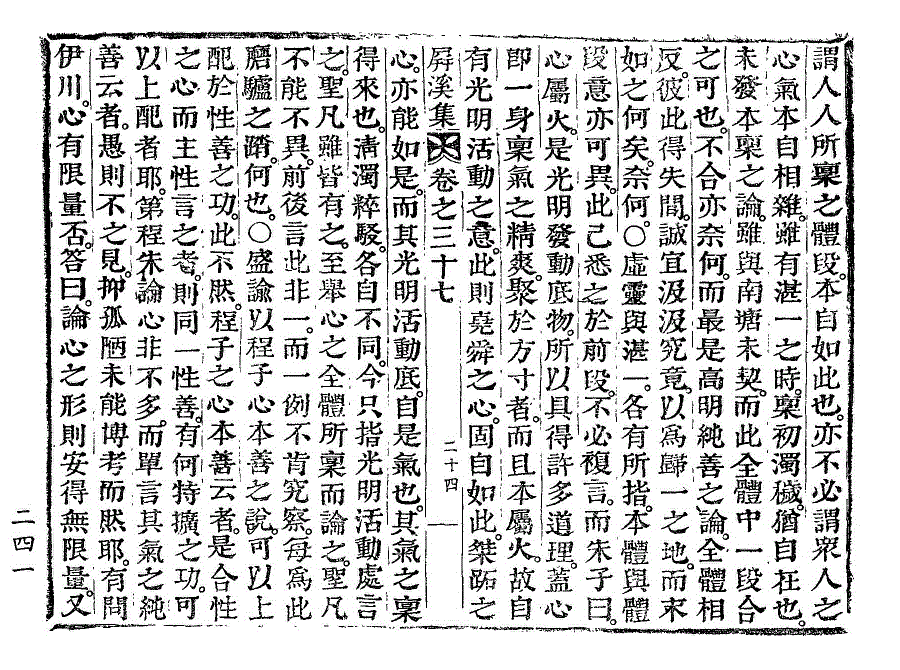 谓人人所禀之体段。本自如此也。亦不必谓众人之心气本自相杂。虽有湛一之时。禀初浊秽。犹自在也。未发本禀之论。虽与南塘未契。而此全体中一段合之可也。不合亦奈何。而最是高明纯善之论。全体相反。彼此得失间。诚宜汲汲究竟。以为归一之地。而末如之何矣。奈何。○虚灵与湛一。各有所指。本体与体段意亦可异。此已悉之于前段。不必复言。而朱子曰。心属火。是光明发动底物。所以具得许多道理。盖心即一身禀气之精爽。聚于方寸者。而且本属火。故自有光明活动之意。此则尧舜之心。固自如此。桀蹠之心。亦能如是。而其光明活动底。自是气也。其气之禀得来也。清浊粹驳。各自不同。今只指光明活动处言之。圣凡虽皆有之。至举心之全体所禀而论之。圣凡不能不异。前后言此非一。而一例不肯究察。每为此磨驴之踏。何也。○盛谕以程子心本善之说。可以上配于性善之功。此不然。程子之心本善云者。是合性之心而主性言之者。则同一性善。有何特扩之功。可以上配者耶。第程朱论心非不多。而单言其气之纯善云者。愚则不之见。抑孤陋未能博考而然耶。有问伊川。心有限量否。答曰。论心之形则安得无限量。又
谓人人所禀之体段。本自如此也。亦不必谓众人之心气本自相杂。虽有湛一之时。禀初浊秽。犹自在也。未发本禀之论。虽与南塘未契。而此全体中一段合之可也。不合亦奈何。而最是高明纯善之论。全体相反。彼此得失间。诚宜汲汲究竟。以为归一之地。而末如之何矣。奈何。○虚灵与湛一。各有所指。本体与体段意亦可异。此已悉之于前段。不必复言。而朱子曰。心属火。是光明发动底物。所以具得许多道理。盖心即一身禀气之精爽。聚于方寸者。而且本属火。故自有光明活动之意。此则尧舜之心。固自如此。桀蹠之心。亦能如是。而其光明活动底。自是气也。其气之禀得来也。清浊粹驳。各自不同。今只指光明活动处言之。圣凡虽皆有之。至举心之全体所禀而论之。圣凡不能不异。前后言此非一。而一例不肯究察。每为此磨驴之踏。何也。○盛谕以程子心本善之说。可以上配于性善之功。此不然。程子之心本善云者。是合性之心而主性言之者。则同一性善。有何特扩之功。可以上配者耶。第程朱论心非不多。而单言其气之纯善云者。愚则不之见。抑孤陋未能博考而然耶。有问伊川。心有限量否。答曰。论心之形则安得无限量。又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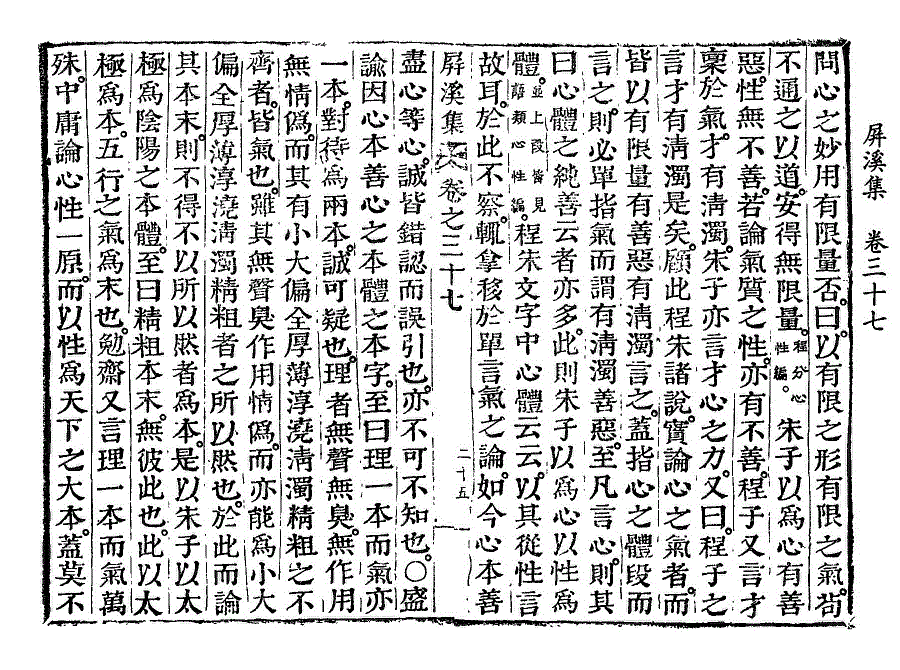 问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气。苟不通之以道。安得无限量。(程分心性编。)朱子以为心有善恶。性无不善。若论气质之性。亦有不善。程子又言才禀于气。才有清浊。朱子亦言才心之力。又曰。程子之言才有清浊是矣。顾此程朱诸说。实论心之气者。而皆以有限量有善恶有清浊言之。盖指心之体段而言之。则必单指气而谓有清浊善恶。至凡言心。则其曰心体之纯善云者亦多。此则朱子以为心以性为体。(并上段皆见语类心性编。)程朱文字中心体云云。以其从性言故耳。于此不察。辄拿移于单言气之论。如今心本善尽心等心。诚皆错认而误引也。亦不可不知也。○盛谕因心本善心之本体之本字。至曰理一本而气亦一本。对待为两本。诚可疑也。理者无声无臭。无作用无情伪。而其有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之不齐者。皆气也。虽其无声臭作用情伪。而亦能为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者之所以然也。于此而论其本末。则不得不以所以然者为本。是以朱子以太极为阴阳之本体。至曰精粗本末。无彼此也。此以太极为本。五行之气为末也。勉斋又言理一本而气万殊。中庸论心性一原。而以性为天下之大本。盖莫不
问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气。苟不通之以道。安得无限量。(程分心性编。)朱子以为心有善恶。性无不善。若论气质之性。亦有不善。程子又言才禀于气。才有清浊。朱子亦言才心之力。又曰。程子之言才有清浊是矣。顾此程朱诸说。实论心之气者。而皆以有限量有善恶有清浊言之。盖指心之体段而言之。则必单指气而谓有清浊善恶。至凡言心。则其曰心体之纯善云者亦多。此则朱子以为心以性为体。(并上段皆见语类心性编。)程朱文字中心体云云。以其从性言故耳。于此不察。辄拿移于单言气之论。如今心本善尽心等心。诚皆错认而误引也。亦不可不知也。○盛谕因心本善心之本体之本字。至曰理一本而气亦一本。对待为两本。诚可疑也。理者无声无臭。无作用无情伪。而其有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之不齐者。皆气也。虽其无声臭作用情伪。而亦能为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者之所以然也。于此而论其本末。则不得不以所以然者为本。是以朱子以太极为阴阳之本体。至曰精粗本末。无彼此也。此以太极为本。五行之气为末也。勉斋又言理一本而气万殊。中庸论心性一原。而以性为天下之大本。盖莫不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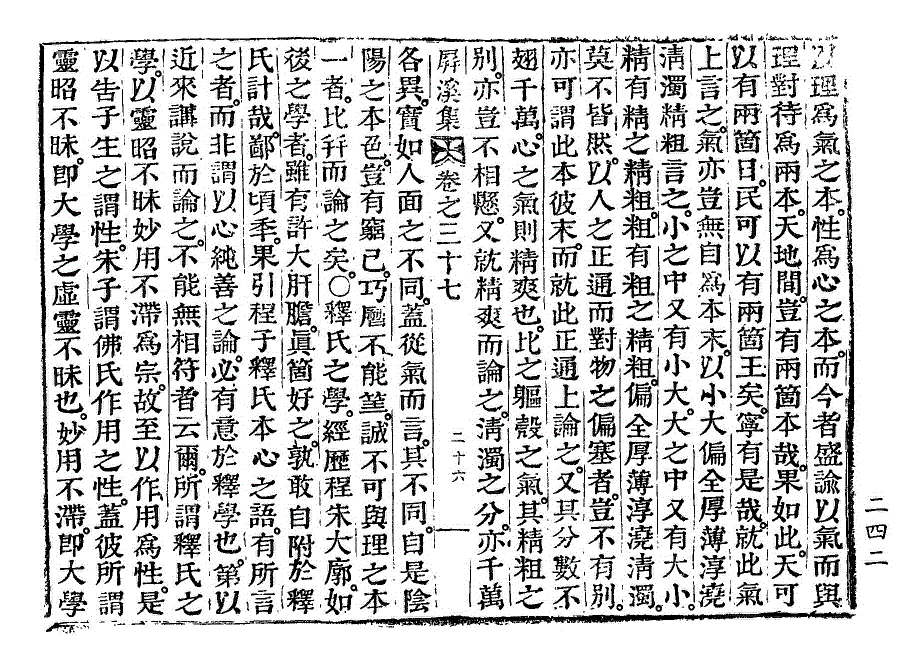 以理为气之本。性为心之本。而今者盛谕以气而与理对待为两本。天地间。岂有两个本哉。果如此。天可以有两个日。民可以有两个王矣。宁有是哉。就此气上言之。气亦岂无自为本末。以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言之。小之中又有小大。大之中又有大小。精有精之精粗。粗有粗之精粗。偏全厚薄淳浇清浊。莫不皆然。以人之正通而对物之偏塞者。岂不有别。亦可谓此本彼末。而就此正通上论之。又其分数不翅千万。心之气则精爽也。比之躯壳之气。其精粗之别。亦岂不相悬。又就精爽而论之。清浊之分。亦千万各异。实如人面之不同。盖从气而言。其不同。自是阴阳之本色。岂有穷已。巧历不能算。诚不可与理之本一者。比并而论之矣。○释氏之学。经历程朱大廓。如后之学者。虽有许大肝胆。真个好之。孰敢自附于释氏计哉。鄙于顷年。果引程子释氏本心之语。有所言之者。而非谓以心纯善之论。必有意于释学也。第以近来讲说而论之。不能无相符者云尔。所谓释氏之学。以灵昭不昧妙用不滞为宗。故至以作用为性。是以告子生之谓性。朱子谓佛氏作用之性。盖彼所谓灵昭不昧。即大学之虚灵不昧也。妙用不滞。即大学
以理为气之本。性为心之本。而今者盛谕以气而与理对待为两本。天地间。岂有两个本哉。果如此。天可以有两个日。民可以有两个王矣。宁有是哉。就此气上言之。气亦岂无自为本末。以小大偏全厚薄淳浇清浊精粗言之。小之中又有小大。大之中又有大小。精有精之精粗。粗有粗之精粗。偏全厚薄淳浇清浊。莫不皆然。以人之正通而对物之偏塞者。岂不有别。亦可谓此本彼末。而就此正通上论之。又其分数不翅千万。心之气则精爽也。比之躯壳之气。其精粗之别。亦岂不相悬。又就精爽而论之。清浊之分。亦千万各异。实如人面之不同。盖从气而言。其不同。自是阴阳之本色。岂有穷已。巧历不能算。诚不可与理之本一者。比并而论之矣。○释氏之学。经历程朱大廓。如后之学者。虽有许大肝胆。真个好之。孰敢自附于释氏计哉。鄙于顷年。果引程子释氏本心之语。有所言之者。而非谓以心纯善之论。必有意于释学也。第以近来讲说而论之。不能无相符者云尔。所谓释氏之学。以灵昭不昧妙用不滞为宗。故至以作用为性。是以告子生之谓性。朱子谓佛氏作用之性。盖彼所谓灵昭不昧。即大学之虚灵不昧也。妙用不滞。即大学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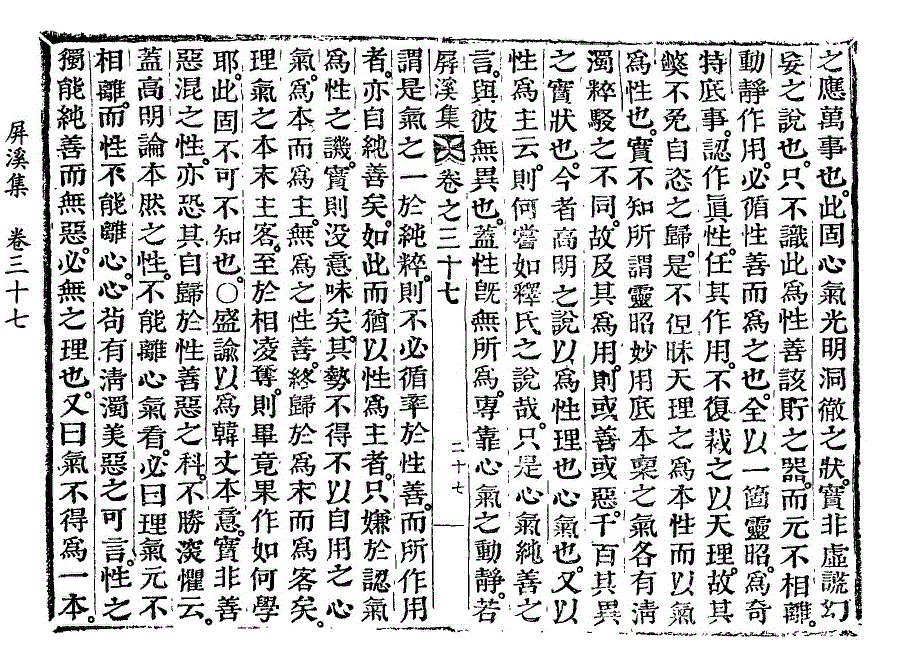 之应万事也。此固心气光明洞彻之状。实非虚谎幻妄之说也。只不识此为性善该贮之器。而元不相离。动静作用。必循性善而为之也。全以一个灵昭。为奇特底事。认作真性。任其作用。不复裁之以天理。故其弊不免自恣之归。是不但昧天理之为本性而以气为性也。实不知所谓灵昭妙用底本禀之气各有清浊粹驳之不同。故及其为用。则或善或恶。千百其异之实状也。今者高明之说以为性理也心气也。又以性为主云。则何尝如释氏之说哉。只是心气纯善之言。与彼无异也。盖性既无所为。专靠心气之动静。若谓是气之一于纯粹。则不必循率于性善。而所作用者。亦自纯善矣。如此而犹以性为主者。只嫌于认气为性之讥。实则没意味矣。其势不得不以自用之心气。为本而为主。无为之性善。终归于为末而为客矣。理气之本末主客。至于相凌夺。则毕竟果作如何学耶。此固不可不知也。○盛谕以为韩丈本意。实非善恶混之性。亦恐其自归于性善恶之科。不胜深惧云。盖高明论本然之性。不能离心气看。必曰理气元不相离。而性不能离心。心苟有清浊美恶之可言。性之独能纯善而无恶。必无之理也。又曰气不得为一本。
之应万事也。此固心气光明洞彻之状。实非虚谎幻妄之说也。只不识此为性善该贮之器。而元不相离。动静作用。必循性善而为之也。全以一个灵昭。为奇特底事。认作真性。任其作用。不复裁之以天理。故其弊不免自恣之归。是不但昧天理之为本性而以气为性也。实不知所谓灵昭妙用底本禀之气各有清浊粹驳之不同。故及其为用。则或善或恶。千百其异之实状也。今者高明之说以为性理也心气也。又以性为主云。则何尝如释氏之说哉。只是心气纯善之言。与彼无异也。盖性既无所为。专靠心气之动静。若谓是气之一于纯粹。则不必循率于性善。而所作用者。亦自纯善矣。如此而犹以性为主者。只嫌于认气为性之讥。实则没意味矣。其势不得不以自用之心气。为本而为主。无为之性善。终归于为末而为客矣。理气之本末主客。至于相凌夺。则毕竟果作如何学耶。此固不可不知也。○盛谕以为韩丈本意。实非善恶混之性。亦恐其自归于性善恶之科。不胜深惧云。盖高明论本然之性。不能离心气看。必曰理气元不相离。而性不能离心。心苟有清浊美恶之可言。性之独能纯善而无恶。必无之理也。又曰气不得为一本。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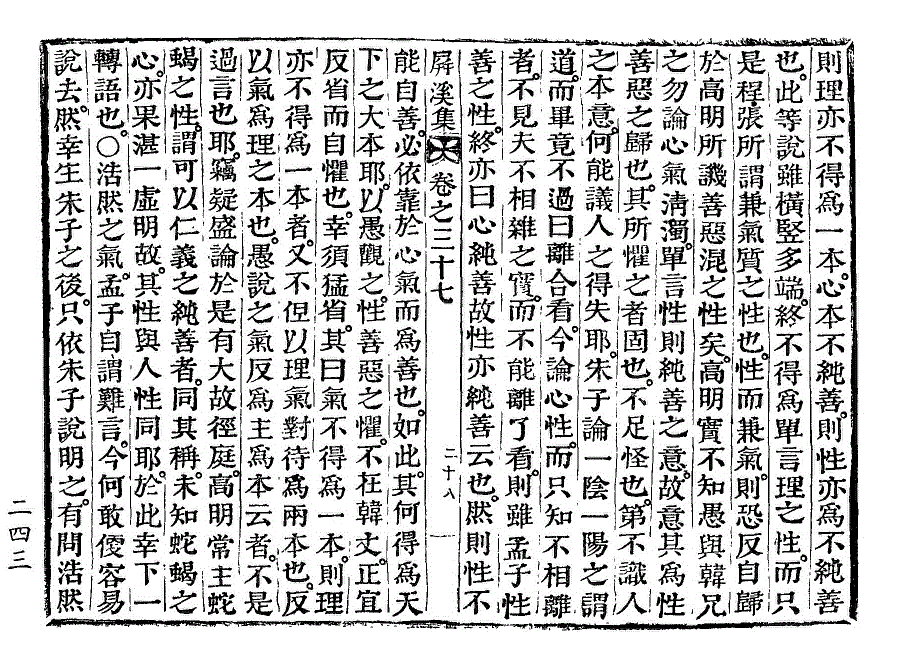 则理亦不得为一本。心本不纯善。则性亦为不纯善也。此等说虽横竖多端。终不得为单言理之性。而只是程,张所谓兼气质之性也。性而兼气。则恐反自归于高明所讥善恶混之性矣。高明实不知愚与韩兄之勿论心气清浊。单言性则纯善之意。故意其为性善恶之归也。其所惧之者固也。不足怪也。第不识人之本意。何能议人之得失耶。朱子论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毕竟不过曰离合看。今论心性。而只知不相离者。不见夫不相杂之实。而不能离了看。则虽孟子性善之性。终亦曰心纯善故性亦纯善云也。然则性不能自善。必依靠于心气而为善也。如此。其何得为天下之大本耶。以愚观之。性善恶之惧。不在韩丈。正宜反省而自惧也。幸须猛省。其曰气不得为一本。则理亦不得为一本者。又不但以理气对待为两本也。反以气为理之本也。愚说之气反为主为本云者。不是过言也耶。窃疑盛论于是有大故径庭。高明常主蛇蝎之性。谓可以仁义之纯善者。同其称。未知蛇蝎之心。亦果湛一虚明故。其性与人性同耶。于此幸下一转语也。○浩然之气。孟子自谓难言。今何敢便容易说去。然幸生朱子之后。只依朱子说明之。有问浩然
则理亦不得为一本。心本不纯善。则性亦为不纯善也。此等说虽横竖多端。终不得为单言理之性。而只是程,张所谓兼气质之性也。性而兼气。则恐反自归于高明所讥善恶混之性矣。高明实不知愚与韩兄之勿论心气清浊。单言性则纯善之意。故意其为性善恶之归也。其所惧之者固也。不足怪也。第不识人之本意。何能议人之得失耶。朱子论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毕竟不过曰离合看。今论心性。而只知不相离者。不见夫不相杂之实。而不能离了看。则虽孟子性善之性。终亦曰心纯善故性亦纯善云也。然则性不能自善。必依靠于心气而为善也。如此。其何得为天下之大本耶。以愚观之。性善恶之惧。不在韩丈。正宜反省而自惧也。幸须猛省。其曰气不得为一本。则理亦不得为一本者。又不但以理气对待为两本也。反以气为理之本也。愚说之气反为主为本云者。不是过言也耶。窃疑盛论于是有大故径庭。高明常主蛇蝎之性。谓可以仁义之纯善者。同其称。未知蛇蝎之心。亦果湛一虚明故。其性与人性同耶。于此幸下一转语也。○浩然之气。孟子自谓难言。今何敢便容易说去。然幸生朱子之后。只依朱子说明之。有问浩然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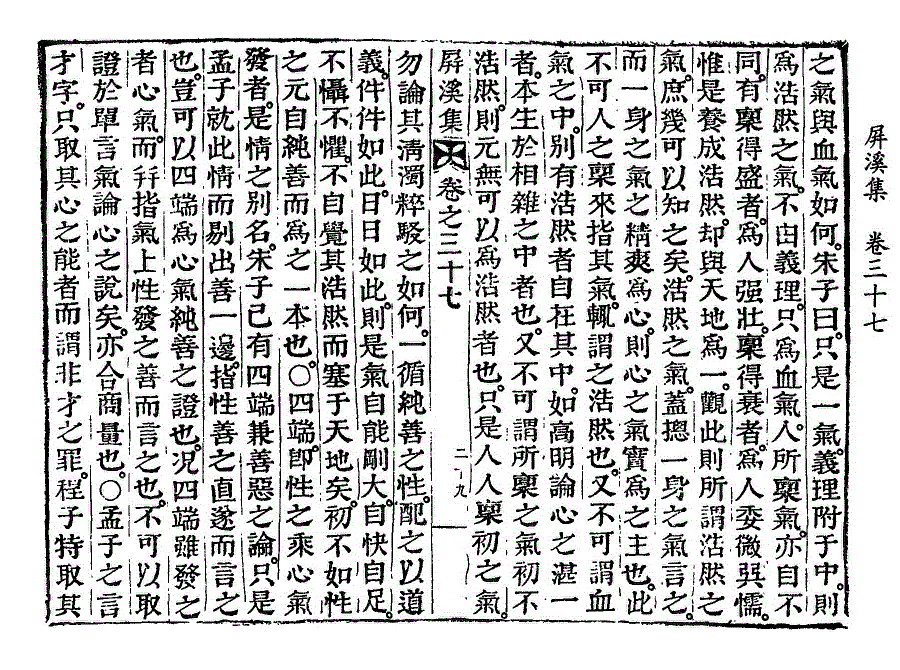 之气与血气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气。义理附于中。则为浩然之气。不由义理。只为血气。人所禀气。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为人强壮。禀得衰者。为人委微巽懦。惟是养成浩然。却与天地为一。观此则所谓浩然之气。庶几可以知之矣。浩然之气。盖总一身之气言之。而一身之气之精爽为心。则心之气实为之主也。此不可人之禀来指其气。辄谓之浩然也。又不可谓血气之中。别有浩然者自在其中。如高明论心之湛一者。本生于相杂之中者也。又不可谓所禀之气初不浩然。则元无可以为浩然者也。只是人人禀初之气。勿论其清浊粹驳之如何。一循纯善之性。配之以道义。件件如此。日日如此。则是气自能刚大。自快自足。不慑不惧。不自觉其浩然而塞于天地矣。初不如性之元自纯善而为之一本也。○四端。即性之乘心气发者。是情之别名。朱子已有四端兼善恶之论。只是孟子就此情而剔出善一边。指性善之直遂而言之也。岂可以四端为心气纯善之證也。况四端虽发之者心气。而并指气上性发之善而言之也。不可以取證于单言气论心之说矣。亦合商量也。○孟子之言才字。只取其心之能者而谓非才之罪。程子特取其
之气与血气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气。义理附于中。则为浩然之气。不由义理。只为血气。人所禀气。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为人强壮。禀得衰者。为人委微巽懦。惟是养成浩然。却与天地为一。观此则所谓浩然之气。庶几可以知之矣。浩然之气。盖总一身之气言之。而一身之气之精爽为心。则心之气实为之主也。此不可人之禀来指其气。辄谓之浩然也。又不可谓血气之中。别有浩然者自在其中。如高明论心之湛一者。本生于相杂之中者也。又不可谓所禀之气初不浩然。则元无可以为浩然者也。只是人人禀初之气。勿论其清浊粹驳之如何。一循纯善之性。配之以道义。件件如此。日日如此。则是气自能刚大。自快自足。不慑不惧。不自觉其浩然而塞于天地矣。初不如性之元自纯善而为之一本也。○四端。即性之乘心气发者。是情之别名。朱子已有四端兼善恶之论。只是孟子就此情而剔出善一边。指性善之直遂而言之也。岂可以四端为心气纯善之證也。况四端虽发之者心气。而并指气上性发之善而言之也。不可以取證于单言气论心之说矣。亦合商量也。○孟子之言才字。只取其心之能者而谓非才之罪。程子特取其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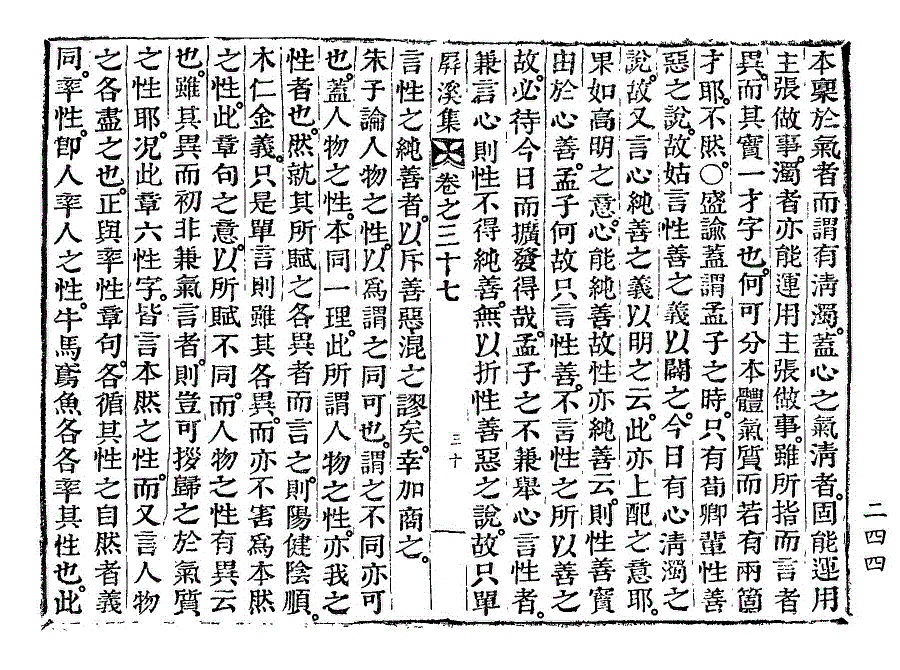 本禀于气者而谓有清浊。盖心之气清者。固能运用主张做事。浊者亦能运用主张做事。虽所指而言者异。而其实一才字也。何可分本体气质而若有两个才耶。不然。○盛谕盖谓孟子之时。只有荀卿辈性善恶之说。故姑言性善之义以辟之。今日有心清浊之说。故又言心纯善之义以明之云。此亦上配之意耶。果如高明之意。心能纯善故性亦纯善云。则性善实由于心善。孟子何故只言性善。不言性之所以善之故。必待今日而扩发得哉。孟子之不兼举心言性者。兼言心则性不得纯善。无以折性善恶之说。故只单言性之纯善者。以斥善恶混之谬矣。幸加商之。
本禀于气者而谓有清浊。盖心之气清者。固能运用主张做事。浊者亦能运用主张做事。虽所指而言者异。而其实一才字也。何可分本体气质而若有两个才耶。不然。○盛谕盖谓孟子之时。只有荀卿辈性善恶之说。故姑言性善之义以辟之。今日有心清浊之说。故又言心纯善之义以明之云。此亦上配之意耶。果如高明之意。心能纯善故性亦纯善云。则性善实由于心善。孟子何故只言性善。不言性之所以善之故。必待今日而扩发得哉。孟子之不兼举心言性者。兼言心则性不得纯善。无以折性善恶之说。故只单言性之纯善者。以斥善恶混之谬矣。幸加商之。朱子论人物之性。以为谓之同可也。谓之不同亦可也。盖人物之性。本同一理。此所谓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也。然就其所赋之各异者而言之。则阳健阴顺。木仁金义。只是单言则虽其各异。而亦不害为本然之性。此章句之意。以所赋不同。而人物之性有异云也。虽其异而初非兼气言者。则岂可拶归之于气质之性耶。况此章六性字。皆言本然之性。而又言人物之各尽之也。正与率性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者义同。率性。即人率人之性。牛马鸢鱼各各率其性也。此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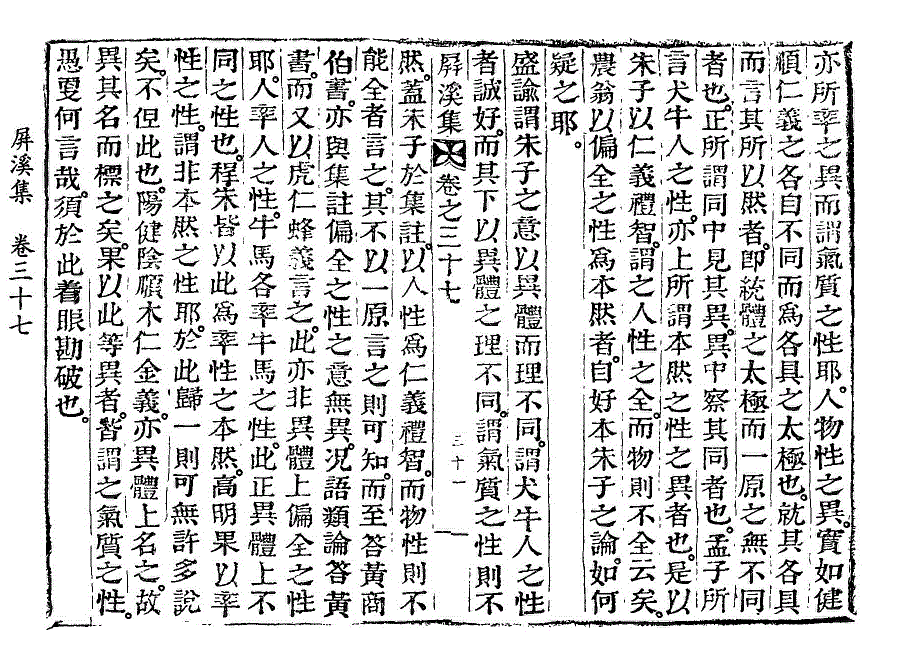 亦所率之异而谓气质之性耶。人物性之异。实如健顺仁义之各自不同而为各具之太极也。就其各具而言其所以然者。即统体之太极而一原之无不同者也。正所谓同中见其异。异中察其同者也。孟子所言犬牛人之性。亦上所谓本然之性之异者也。是以朱子以仁义礼智。谓之人性之全。而物则不全云矣。农翁以偏全之性为本然者。自好本朱子之论。如何疑之耶。
亦所率之异而谓气质之性耶。人物性之异。实如健顺仁义之各自不同而为各具之太极也。就其各具而言其所以然者。即统体之太极而一原之无不同者也。正所谓同中见其异。异中察其同者也。孟子所言犬牛人之性。亦上所谓本然之性之异者也。是以朱子以仁义礼智。谓之人性之全。而物则不全云矣。农翁以偏全之性为本然者。自好本朱子之论。如何疑之耶。盛谕谓朱子之意以异体而理不同。谓犬牛人之性者诚好。而其下以异体之理不同。谓气质之性则不然。盖朱子于集注。以人性为仁义礼智。而物性则不能全者言之。其不以一原言之则可知。而至答黄商伯书。亦与集注偏全之性之意无异。况语类论答黄书。而又以虎仁蜂义言之。此亦非异体上偏全之性耶。人率人之性。牛马各率牛马之性。此正异体上不同之性也。程,朱皆以此为率性之本然。高明果以率性之性。谓非本然之性耶。于此归一则可无许多说矣。不但此也。阳健阴顺木仁金义。亦异体上名之。故异其名而标之矣。果以此等异者。皆谓之气质之性。愚更何言哉。须于此着眼勘破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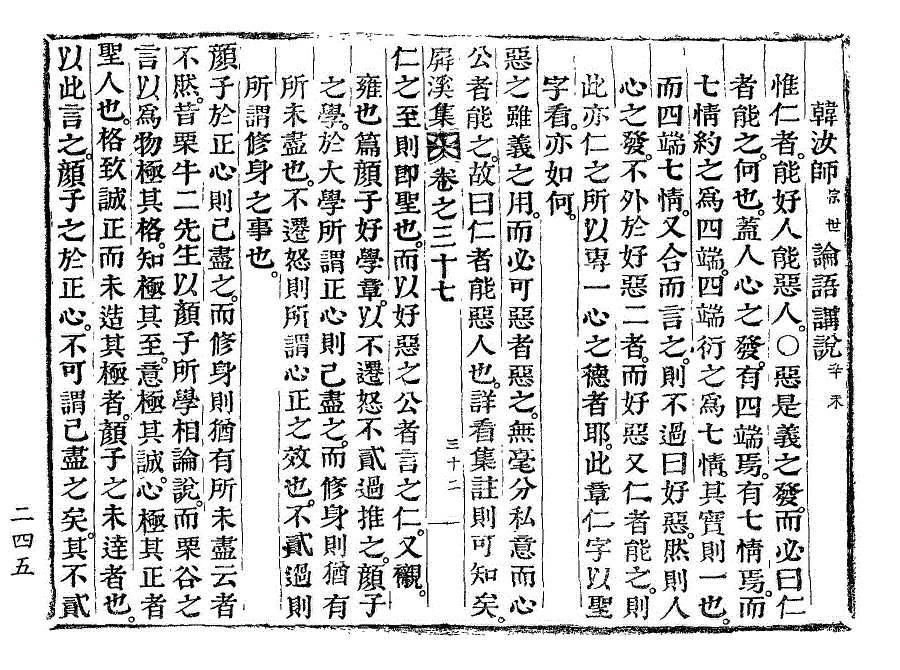 韩汝师(宗世)论语讲说(辛未)
韩汝师(宗世)论语讲说(辛未)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是义之发。而必曰仁者能之。何也。盖人心之发。有四端焉。有七情焉。而七情约之为四端。四端衍之为七情。其实则一也。而四端七情。又合而言之。则不过曰好恶。然则人心之发。不外于好恶二者。而好恶又仁者能之。则此亦仁之所以专一心之德者耶。此章仁字以圣字看。亦如何。
恶之虽义之用。而必可恶者恶之。无毫分私意而心公者能之。故曰仁者能恶人也。详看集注则可知矣。仁之至则即圣也。而以好恶之公者言之仁。又衬。
雍也篇颜子好学章。以不迁怒不贰过推之。颜子之学。于大学所谓正心则已尽之。而修身则犹有所未尽也。不迁怒则所谓心正之效也。不贰过则所谓修身之事也。
颜子于正心则已尽之。而修身则犹有所未尽云者不然。昔栗牛二先生以颜子所学相论说。而栗谷之言以为物极其格。知极其至。意极其诚。心极其正者圣人也。格致诚正而未造其极者。颜子之未达者也。以此言之。颜子之于正心。不可谓已尽之矣。其不贰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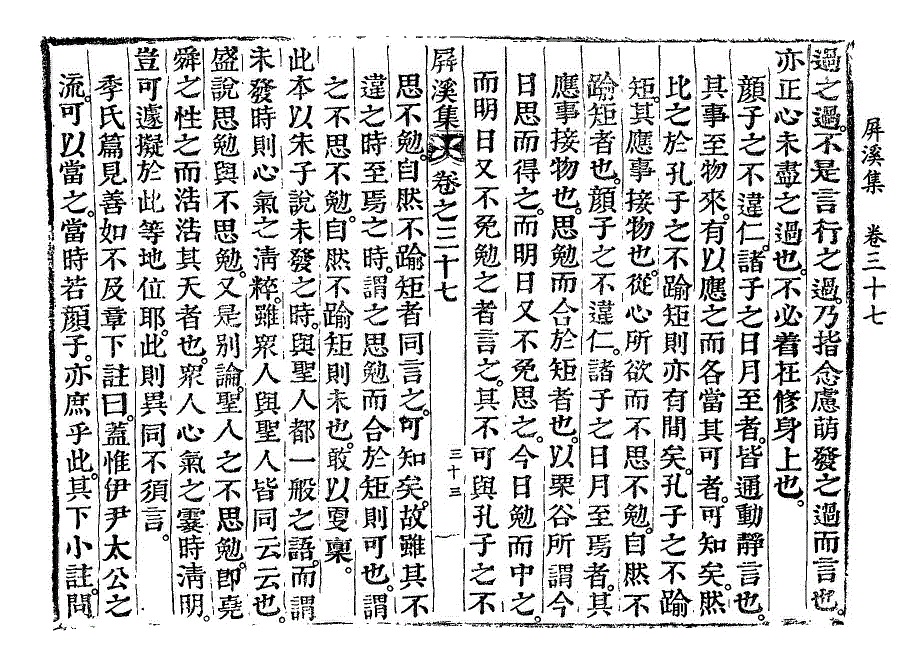 过之过。不是言行之过。乃指念虑萌发之过而言也。亦正心未尽之过也。不必着在修身上也。
过之过。不是言行之过。乃指念虑萌发之过而言也。亦正心未尽之过也。不必着在修身上也。颜子之不违仁。诸子之日月至者。皆通动静言也。其事至物来。有以应之而各当其可者。可知矣。然比之于孔子之不踰矩则亦有间矣。孔子之不踰矩。其应事接物也。从心所欲而不思不勉。自然不踰矩者也。颜子之不违仁。诸子之日月至焉者。其应事接物也。思勉而合于矩者也。以栗谷所谓今日思而得之。而明日又不免思之。今日勉而中之。而明日又不免勉之者言之。其不可与孔子之不思不勉。自然不踰矩者同言之。可知矣。故虽其不违之时至焉之时。谓之思勉而合于矩则可也。谓之不思不勉。自然不踰矩则未也。敢以更禀。
此本以朱子说未发之时。与圣人都一般之语。而谓未发时则心气之清粹。虽众人与圣人皆同云云也。盛说思勉与不思勉。又是别论。圣人之不思勉。即尧舜之性之而浩浩其天者也。众人心气之霎时清明。岂可遽拟于此等地位耶。此则异同不须言。
季氏篇见善如不及章下注曰。盖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当之。当时若颜子。亦庶乎此。其下小注。问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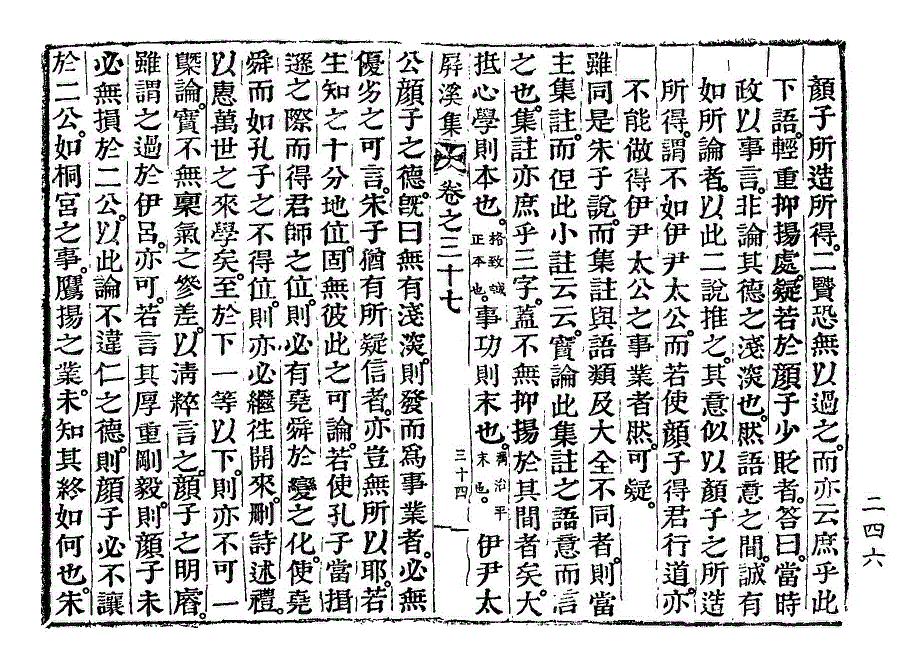 颜子所造所得。二贤恐无以过之。而亦云庶乎此下语。轻重抑扬处。疑若于颜子少贬者。答曰。当时政以事言。非论其德之浅深也。然语意之间。诚有如所论者。以此二说推之。其意似以颜子之所造所得。谓不如伊尹,太公。而若使颜子得君行道。亦不能做得伊尹,太公之事业者然。可疑。
颜子所造所得。二贤恐无以过之。而亦云庶乎此下语。轻重抑扬处。疑若于颜子少贬者。答曰。当时政以事言。非论其德之浅深也。然语意之间。诚有如所论者。以此二说推之。其意似以颜子之所造所得。谓不如伊尹,太公。而若使颜子得君行道。亦不能做得伊尹,太公之事业者然。可疑。虽同是朱子说。而集注与语类及大全不同者。则当主集注。而但此小注云云。实论此集注之语意而言之也。集注亦庶乎三字。盖不无抑扬于其间者矣。大抵心学则本也。(格致诚正本也。)事功则末也。(齐治平末也。)伊尹,太公,颜子之德。既曰无有浅深。则发而为事业者。必无优劣之可言。朱子犹有所疑信者。亦岂无所以耶。若生知之十分地位。固无彼此之可论。若使孔子当揖逊之际而得君师之位。则必有尧舜于变之化。使尧舜而如孔子之不得位。则亦必继往开来。删诗述礼。以惠万世之来学矣。至于下一等以下。则亦不可一槩论。实不无禀气之参差。以清粹言之。颜子之明睿。虽谓之过于伊吕。亦可。若言其厚重刚毅。则颜子未必无损于二公。以此论不违仁之德。则颜子必不让于二公。如桐宫之事。鹰扬之业。未知其终如何也。朱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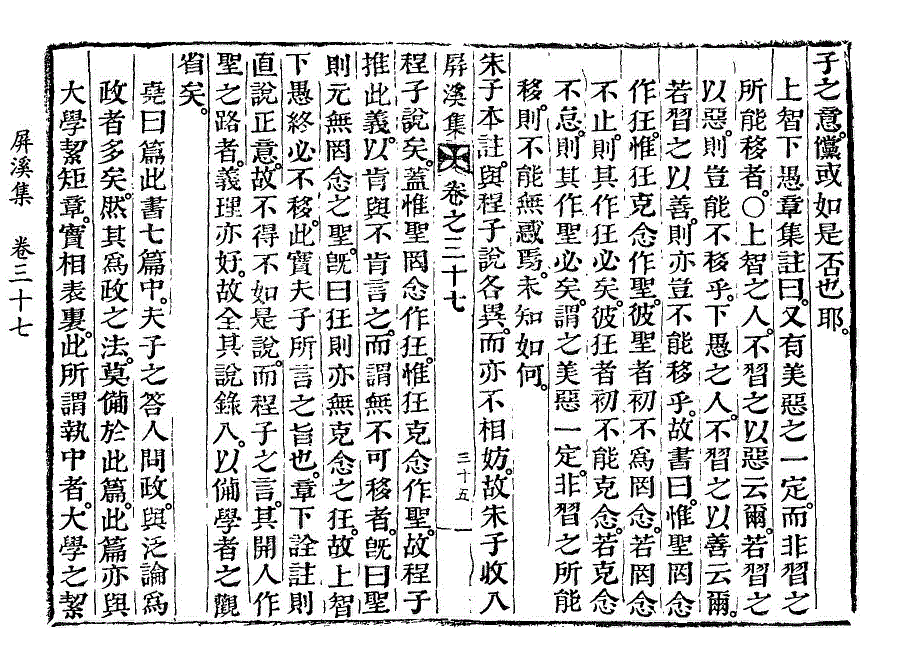 子之意。傥或如是否也耶。
子之意。傥或如是否也耶。上智下愚章集注曰。又有美恶之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上智之人。不习之以恶云尔。若习之以恶。则岂能不移乎。下愚之人。不习之以善云尔。若习之以善。则亦岂不能移乎。故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彼圣者初不为罔念。若罔念不止。则其作狂必矣。彼狂者初不能克念。若克念不怠。则其作圣必矣。谓之美恶一定。非习之所能移。则不能无惑焉。未知如何。
朱子本注。与程子说各异。而亦不相妨。故朱子收入程子说矣。盖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故程子推此义。以肯与不肯言之。而谓无不可移者。既曰圣则元无罔念之圣。既曰狂则亦无克念之狂。故上智下愚终必不移。此实夫子所言之旨也。章下诠注则直说正意。故不得不如是说。而程子之言。其开人作圣之路者。义理亦好。故全其说录入。以备学者之观省矣。
尧曰篇此书七篇中。夫子之答人问政。与泛论为政者多矣。然其为政之法。莫备于此篇。此篇亦与大学絜矩章。实相表里。此所谓执中者。大学之絜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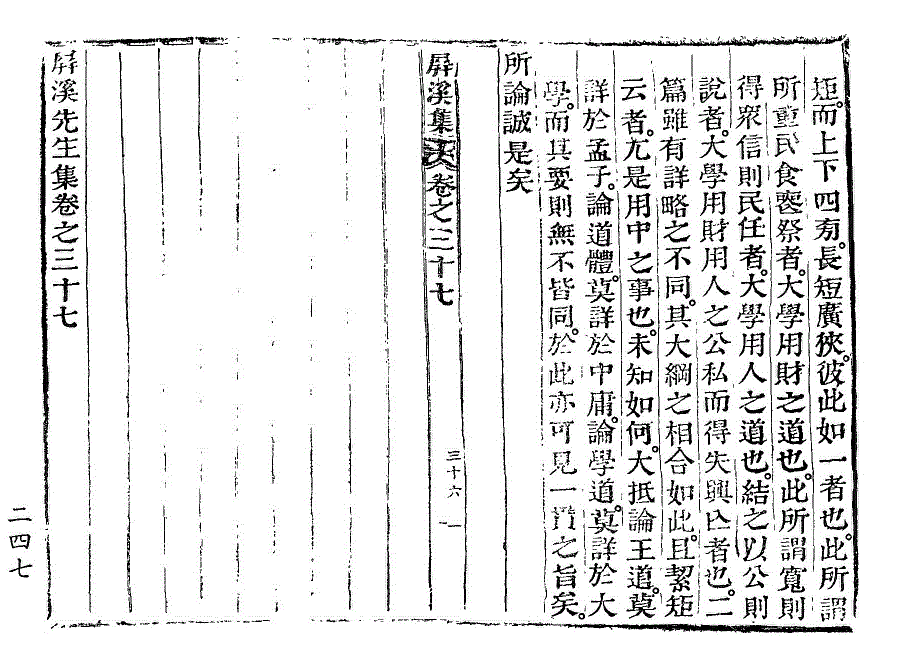 矩。而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者也。此所谓所重民食丧祭者。大学用财之道也。此所谓宽则得众信则民任者。大学用人之道也。结之以公则说者。大学用财用人之公私而得失兴亡者也。二篇虽有详略之不同。其大纲之相合如此。且絜矩云者。尤是用中之事也。未知如何。大抵论王道。莫详于孟子。论道体。莫详于中庸。论学道。莫详于大学。而其要则无不皆同。于此亦可见一贯之旨矣。
矩。而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者也。此所谓所重民食丧祭者。大学用财之道也。此所谓宽则得众信则民任者。大学用人之道也。结之以公则说者。大学用财用人之公私而得失兴亡者也。二篇虽有详略之不同。其大纲之相合如此。且絜矩云者。尤是用中之事也。未知如何。大抵论王道。莫详于孟子。论道体。莫详于中庸。论学道。莫详于大学。而其要则无不皆同。于此亦可见一贯之旨矣。所论诚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