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书
书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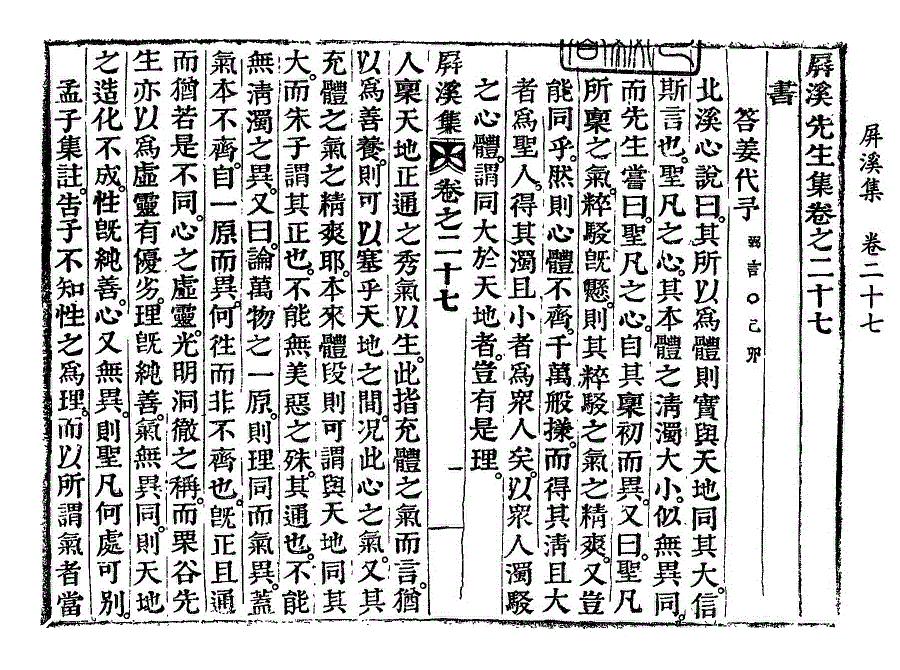 答姜代予(弼言○己卯)
答姜代予(弼言○己卯)北溪心说曰。其所以为体则实与天地同其大。信斯言也。圣凡之心。其本体之清浊大小。似无异同。而先生尝曰。圣凡之心。自其禀初而异。又曰。圣凡所禀之气。粹驳既悬。则其粹驳之气之精爽。又岂能同乎。然则心体不齐。千万般㨾。而得其清且大者为圣人。得其浊且小者为众人矣。以众人浊驳之心体。谓同大于天地者。岂有是理。
人禀天地正通之秀气以生。此指充体之气而言。犹以为善养。则可以塞乎天地之间。况此心之气。又其充体之气之精爽耶。本来体段则可谓与天地同其大。而朱子谓其正也。不能无美恶之殊。其通也。不能无清浊之异。又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盖气本不齐。自一原而异。何往而非不齐也。既正且通而犹若是不同。心之虚灵。光明洞彻之称。而栗谷先生亦以为虚灵有优劣。理既纯善。气无异同。则天地之造化不成。性既纯善。心又无异。则圣凡何处可别。
孟子集注。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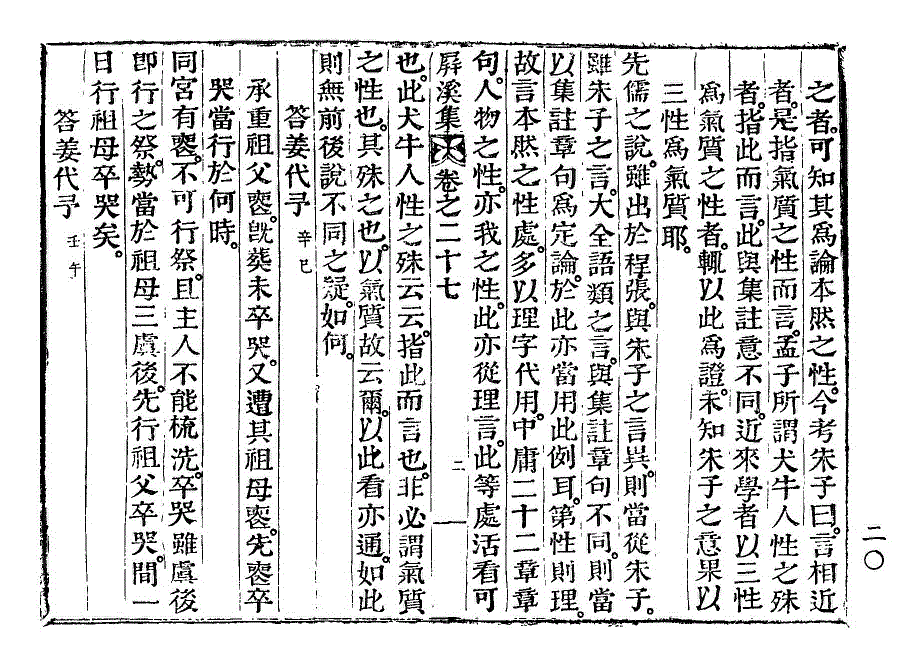 之者。可知其为论本然之性。今考朱子曰。言相近者。是指气质之性而言。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者。指此而言。此与集注意不同。近来学者以三性为气质之性者。辄以此为證。未知朱子之意果以三性为气质耶。
之者。可知其为论本然之性。今考朱子曰。言相近者。是指气质之性而言。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者。指此而言。此与集注意不同。近来学者以三性为气质之性者。辄以此为證。未知朱子之意果以三性为气质耶。先儒之说。虽出于程,张。与朱子之言异。则当从朱子。虽朱子之言。大全语类之言。与集注章句不同。则当以集注章句为定论。于此亦当用此例耳。第性则理。故言本然之性处。多以理字代用。中庸二十二章章句。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亦从理言。此等处活看可也。此犬牛人性之殊云云。指此而言也。非必谓气质之性也。其殊之也。以气质故云尔。以此看亦通。如此则无前后说不同之疑。如何。
答姜代予(辛巳)
承重祖父丧。既葬未卒哭。又遭其祖母丧。先丧卒哭当行于何时。
同宫有丧。不可行祭。且主人不能梳洗。卒哭虽虞后即行之祭。势当于祖母三虞后。先行祖父卒哭。间一日行祖母卒哭矣。
答姜代予(壬午)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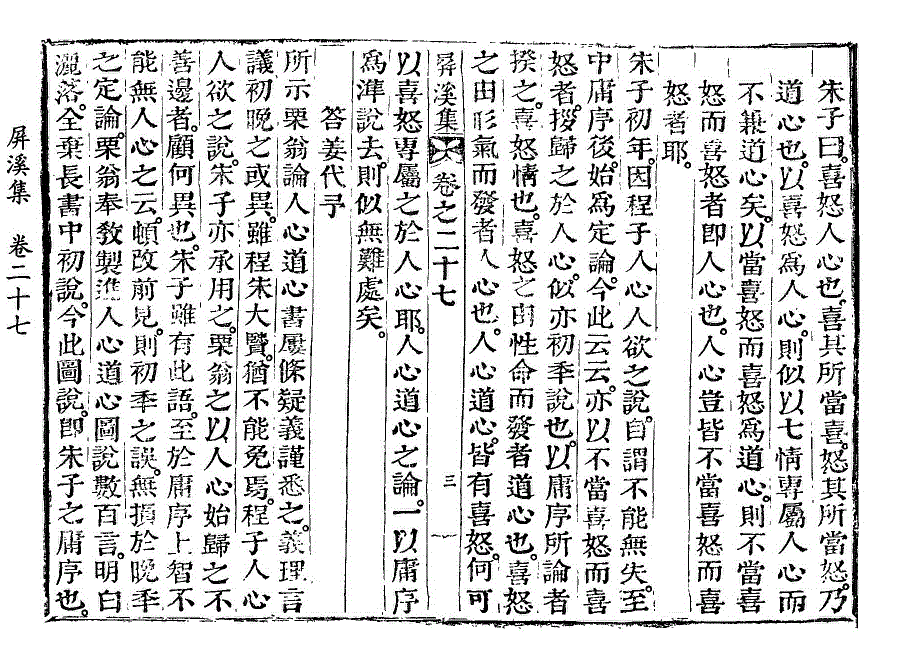 朱子曰。喜怒人心也。喜其所当喜。怒其所当怒。乃道心也。以喜怒为人心。则似以七情专属人心而不兼道心矣。以当喜怒而喜怒为道心。则不当喜怒而喜怒者即人心也。人心岂皆不当喜怒而喜怒者耶。
朱子曰。喜怒人心也。喜其所当喜。怒其所当怒。乃道心也。以喜怒为人心。则似以七情专属人心而不兼道心矣。以当喜怒而喜怒为道心。则不当喜怒而喜怒者即人心也。人心岂皆不当喜怒而喜怒者耶。朱子初年。因程子人心人欲之说。自谓不能无失。至中庸序后。始为定论。今此云云。亦以不当喜怒而喜怒者。拶归之于人心。似亦初年说也。以庸序所论者揆之。喜怒情也。喜怒之由性命而发者道心也。喜怒之由形气而发者人心也。人心道心。皆有喜怒。何可以喜怒专属之于人心耶。人心道心之论。一以庸序为准说去。则似无难处矣。
答姜代予
所示栗翁论人心道心书屡条疑义谨悉之。义理言议初晚之或异。虽程朱大贤。犹不能免焉。程子人心人欲之说。朱子亦承用之。栗翁之以人心始归之不善边者。顾何异也。朱子虽有此语。至于庸序上智不能无人心之云。顿改前见。则初年之误。无损于晚年之定论。栗翁奉教制进人心道心图说数百言。明白洒落。全弃长书中初说。今此图说。即朱子之庸序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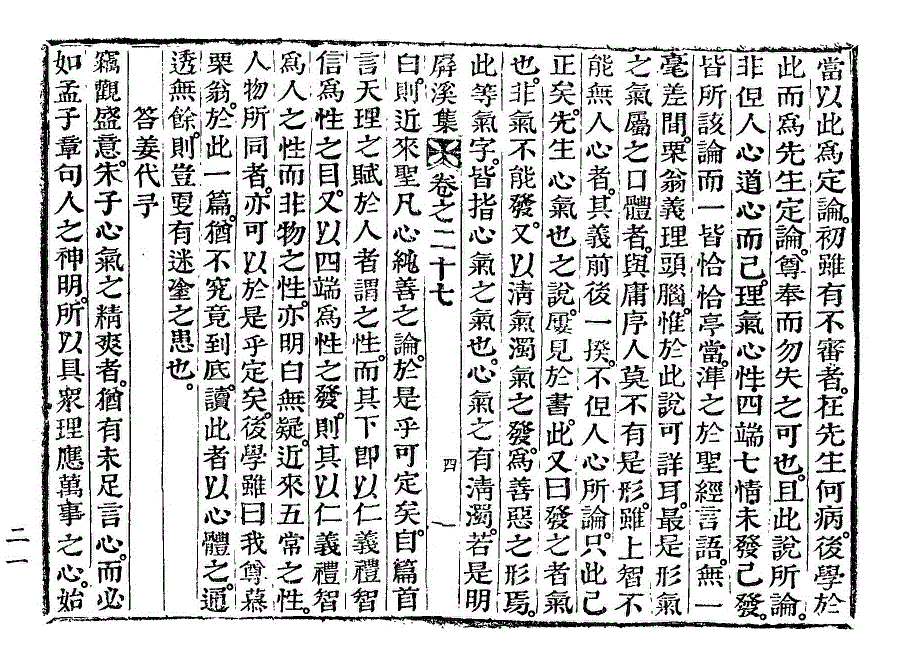 当以此为定论。初虽有不审者。在先生何病。后学于此而为先生定论。尊奉而勿失之可也。且此说所论。非但人心道心而已。理气心性,四端七情,未发已发。皆所该论而一皆恰恰亭当。准之于圣经言语。无一毫差间。栗翁义理头脑。惟于此说可详耳。最是形气之气属之口体者。与庸序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其义前后一揆。不但人心所论。只此已正矣。先生心气也之说。屡见于书。此又曰发之者气也。非气不能发。又以清气浊气之发。为善恶之形焉。此等气字。皆指心气之气也。心气之有清浊。若是明白。则近来圣凡心纯善之论。于是乎可定矣。自篇首言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而其下即以仁义礼智信为性之目。又以四端为性之发。则其以仁义礼智为人之性而非物之性。亦明白无疑。近来五常之性。人物所同者。亦可以于是乎定矣。后学虽曰我尊慕栗翁。于此一篇。犹不究竟到底。读此者以心体之。通透无馀。则岂更有迷涂之患也。
当以此为定论。初虽有不审者。在先生何病。后学于此而为先生定论。尊奉而勿失之可也。且此说所论。非但人心道心而已。理气心性,四端七情,未发已发。皆所该论而一皆恰恰亭当。准之于圣经言语。无一毫差间。栗翁义理头脑。惟于此说可详耳。最是形气之气属之口体者。与庸序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其义前后一揆。不但人心所论。只此已正矣。先生心气也之说。屡见于书。此又曰发之者气也。非气不能发。又以清气浊气之发。为善恶之形焉。此等气字。皆指心气之气也。心气之有清浊。若是明白。则近来圣凡心纯善之论。于是乎可定矣。自篇首言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而其下即以仁义礼智信为性之目。又以四端为性之发。则其以仁义礼智为人之性而非物之性。亦明白无疑。近来五常之性。人物所同者。亦可以于是乎定矣。后学虽曰我尊慕栗翁。于此一篇。犹不究竟到底。读此者以心体之。通透无馀。则岂更有迷涂之患也。答姜代予
窃观盛意。朱子心气之精爽者。犹有未足言心。而必如孟子章句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之心。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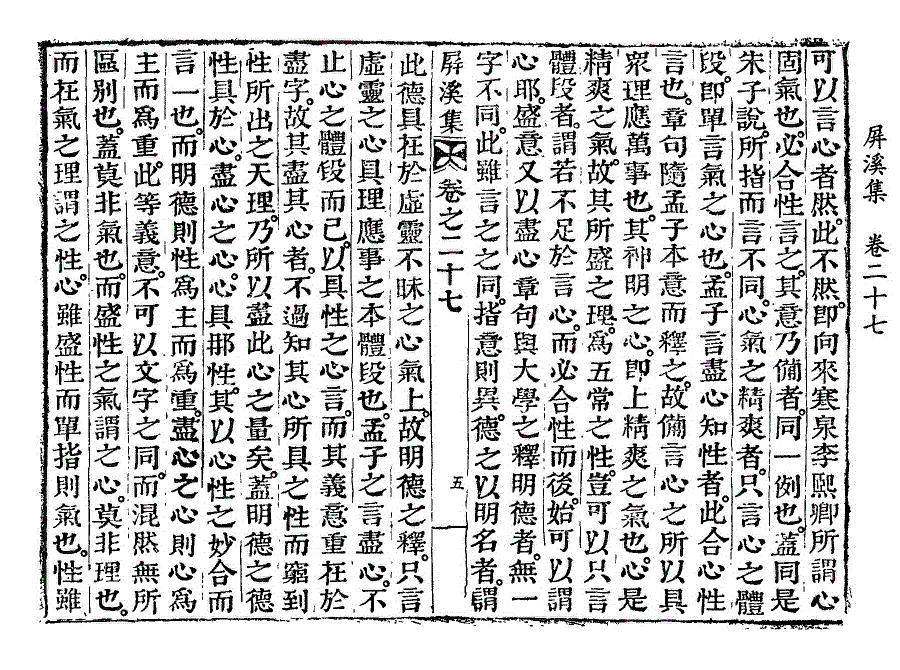 可以言心者然。此不然。即向来寒泉李熙卿所谓心固气也。必合性言之。其意乃备者。同一例也。盖同是朱子说。所指而言不同。心气之精爽者。只言心之体段。即单言气之心也。孟子言尽心知性者。此合心性言也。章句随孟子本意而释之。故备言心之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也。其神明之心。即上精爽之气也。心是精爽之气。故其所盛之理。为五常之性。岂可以只言体段者。谓若不足于言心。而必合性而后。始可以谓心耶。盛意又以尽心章句与大学之释明德者。无一字不同。此虽言之之同。指意则异。德之以明名者。谓此德具在于虚灵不昧之心气上。故明德之释。只言虚灵之心具理应事之本体段也。孟子之言尽心。不止心之体段而已。以具性之心言。而其义意重在于尽字。故其尽其心者。不过知其心所具之性而穷到性所出之天理。乃所以尽此心之量矣。盖明德之德性具于心。尽心之心。心具那性。其以心性之妙合而言一也。而明德则性为主而为重。尽心之心则心为主而为重。此等义意。不可以文字之同。而混然无所区别也。盖莫非气也。而盛性之气谓之心。莫非理也。而在气之理谓之性。心虽盛性而单指则气也。性虽
可以言心者然。此不然。即向来寒泉李熙卿所谓心固气也。必合性言之。其意乃备者。同一例也。盖同是朱子说。所指而言不同。心气之精爽者。只言心之体段。即单言气之心也。孟子言尽心知性者。此合心性言也。章句随孟子本意而释之。故备言心之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也。其神明之心。即上精爽之气也。心是精爽之气。故其所盛之理。为五常之性。岂可以只言体段者。谓若不足于言心。而必合性而后。始可以谓心耶。盛意又以尽心章句与大学之释明德者。无一字不同。此虽言之之同。指意则异。德之以明名者。谓此德具在于虚灵不昧之心气上。故明德之释。只言虚灵之心具理应事之本体段也。孟子之言尽心。不止心之体段而已。以具性之心言。而其义意重在于尽字。故其尽其心者。不过知其心所具之性而穷到性所出之天理。乃所以尽此心之量矣。盖明德之德性具于心。尽心之心。心具那性。其以心性之妙合而言一也。而明德则性为主而为重。尽心之心则心为主而为重。此等义意。不可以文字之同。而混然无所区别也。盖莫非气也。而盛性之气谓之心。莫非理也。而在气之理谓之性。心虽盛性而单指则气也。性虽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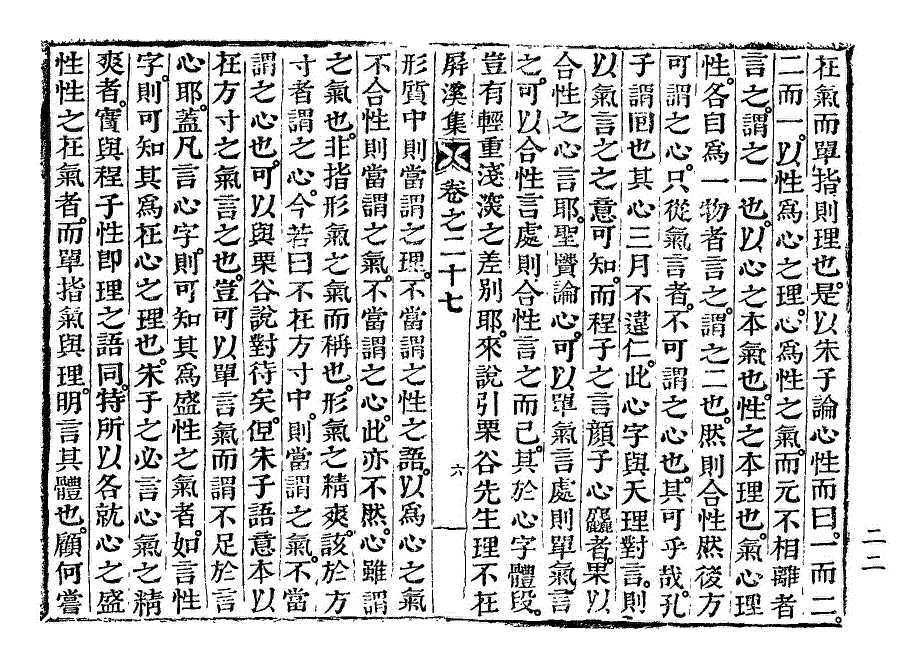 在气而单指则理也。是以朱子论心性而曰。一而二。二而一。以性为心之理。心为性之气。而元不相离者言之。谓之一也。以心之本气也。性之本理也。气心理性。各自为一物者言之。谓之二也。然则合性然后方可谓之心。只从气言者。不可谓之心也。其可乎哉。孔子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此心字与天理对言。则以气言之之意可知。而程子之言颜子心粗者。果以合性之心言耶。圣贤论心。可以单气言处则单气言之。可以合性言处则合性言之而已。其于心字体段。岂有轻重浅深之差别耶。来说引栗谷先生理不在形质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之语。以为心之气不合性则当谓之气。不当谓之心。此亦不然。心虽谓之气也。非指形气之气而称也。形气之精爽。该于方寸者谓之心。今若曰不在方寸中。则当谓之气。不当谓之心也。可以与栗谷说对待矣。但朱子语意本以在方寸之气言之也。岂可以单言气而谓不足于言心耶。盖凡言心字。则可知其为盛性之气者。如言性字。则可知其为在心之理也。朱子之必言心气之精爽者。实与程子性即理之语同。特所以各就心之盛性性之在气者。而单指气与理。明言其体也。顾何尝
在气而单指则理也。是以朱子论心性而曰。一而二。二而一。以性为心之理。心为性之气。而元不相离者言之。谓之一也。以心之本气也。性之本理也。气心理性。各自为一物者言之。谓之二也。然则合性然后方可谓之心。只从气言者。不可谓之心也。其可乎哉。孔子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此心字与天理对言。则以气言之之意可知。而程子之言颜子心粗者。果以合性之心言耶。圣贤论心。可以单气言处则单气言之。可以合性言处则合性言之而已。其于心字体段。岂有轻重浅深之差别耶。来说引栗谷先生理不在形质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之语。以为心之气不合性则当谓之气。不当谓之心。此亦不然。心虽谓之气也。非指形气之气而称也。形气之精爽。该于方寸者谓之心。今若曰不在方寸中。则当谓之气。不当谓之心也。可以与栗谷说对待矣。但朱子语意本以在方寸之气言之也。岂可以单言气而谓不足于言心耶。盖凡言心字。则可知其为盛性之气者。如言性字。则可知其为在心之理也。朱子之必言心气之精爽者。实与程子性即理之语同。特所以各就心之盛性性之在气者。而单指气与理。明言其体也。顾何尝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3H 页
 心必去所盛之性而单言气也。性必去所在之气而单言理也。近来主心纯善之说。本不与释氏认气为性者同。而只知心性不相离为一之义。不复知离看则性本理心本气为二之实。若闻心即气之精爽。清浊粹驳等语。则必举本心良心本善等主性言之之心。以为圣凡之心同于纯善。反以主气言心斥之。心性头颅之义。终焉不明。鄙人为是之辨。与人论说。多在于单言气一边而已。亦何尝遗却合性之本体耶。此正与反斥以主气者同一意也。皆不相知之说也。盛说且以局定之气禀。止盛性而流行者也。盛意谓圣凡精爽。非无清浊之分。而其所以虚灵所以光明。皆性之为也。此亦不然。盖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今言先有此虚灵光明底理。故有此虚灵光明之气云。则诚可矣。至曰心之气以具五性。故能虚灵光明。此却倒说。朱子之言曰。灵处是心。不是性。又曰。能觉者气之灵。凡气之体段。正偏清浊极多般。而心是正通之精爽。自能虚灵光明。故其所具之性亦粹然。而五常之性灿然矣。幸商之。
心必去所盛之性而单言气也。性必去所在之气而单言理也。近来主心纯善之说。本不与释氏认气为性者同。而只知心性不相离为一之义。不复知离看则性本理心本气为二之实。若闻心即气之精爽。清浊粹驳等语。则必举本心良心本善等主性言之之心。以为圣凡之心同于纯善。反以主气言心斥之。心性头颅之义。终焉不明。鄙人为是之辨。与人论说。多在于单言气一边而已。亦何尝遗却合性之本体耶。此正与反斥以主气者同一意也。皆不相知之说也。盛说且以局定之气禀。止盛性而流行者也。盛意谓圣凡精爽。非无清浊之分。而其所以虚灵所以光明。皆性之为也。此亦不然。盖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今言先有此虚灵光明底理。故有此虚灵光明之气云。则诚可矣。至曰心之气以具五性。故能虚灵光明。此却倒说。朱子之言曰。灵处是心。不是性。又曰。能觉者气之灵。凡气之体段。正偏清浊极多般。而心是正通之精爽。自能虚灵光明。故其所具之性亦粹然。而五常之性灿然矣。幸商之。答姜代予
中庸戒慎恐惧。即静时工夫。而沙溪先生以兼动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3L 页
 静言之。以朱子答胡季随戒惧属静。为初年说。但以集注观之。恐无兼动静意。未知如何。
静言之。以朱子答胡季随戒惧属静。为初年说。但以集注观之。恐无兼动静意。未知如何。沙溪先生讲说。元来的确精深。而况辨疑所载。即慎斋与两宋先生考校整顿。宜无可疑。而此戒慎恐惧兼动静之说。终不能无疑。今以本文子思之意言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是兼动静说。而下句将言不睹闻时戒惧。故先以须臾说起。以动静言之。静是须臾时也。因下是故字。以言戒惧于不睹闻时云。则文势精神处。其不在于静时耶。以字义言之。慎独之慎。戒慎之慎。同一慎字。而其属动属静。只在于不睹闻与独知之时。今言慎之于不睹闻。则不睹闻是未发故属静。独知是心之萌发。故慎之于独知之时。则属之动者。十分当然。章句常存敬畏。盖谓戒慎字义。本兼动静言者。而注释之体。敷衍以说。故为言学者治心之工。常存敬畏。而虽不见闻。亦不敢忽。其不见闻而不敢忽者。正释此属静之意。而终归之于存养工夫。朱子之以戒慎慎独分动静说。不独答季随说而已。已自章句而明白无疑矣。末章亦孔之昭。不愧屋漏。子思之意。已分动静说。以结首章动静工夫之意。而此下章句。亦以慎独戒慎分属之。揆之子思朱子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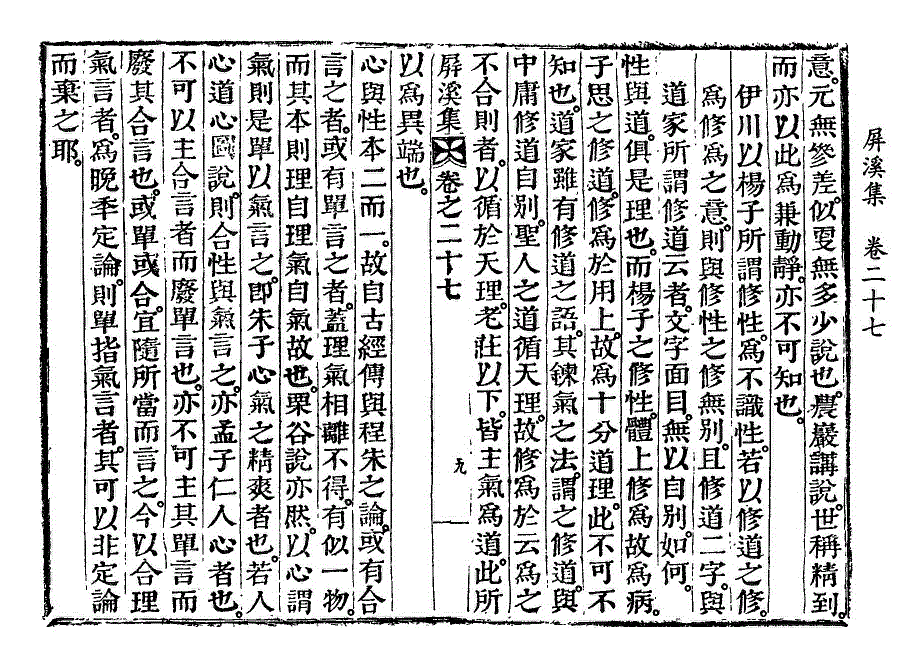 意。元无参差。似更无多少说也。农岩讲说。世称精到。而亦以此为兼动静。亦不可知也。
意。元无参差。似更无多少说也。农岩讲说。世称精到。而亦以此为兼动静。亦不可知也。伊川以杨子所谓修性。为不识性。若以修道之修。为修为之意。则与修性之修无别。且修道二字。与道家所谓修道云者。文字面目。无以自别。如何。
性与道。俱是理也。而杨子之修性。体上修为故为病。子思之修道。修为于用上。故为十分道理。此不可不知也。道家虽有修道之语。其鍊气之法。谓之修道。与中庸修道自别。圣人之道循天理。故修为于云为之不合则者。以循于天理。老庄以下。皆主气为道。此所以为异端也。
心与性本二而一。故自古经传与程朱之论。或有合言之者。或有单言之者。盖理气相离不得。有似一物。而其本则理自理气自气故也。栗谷说亦然。以心谓气则是单以气言之。即朱子心气之精爽者也。若人心道心图说。则合性与气言之。亦孟子仁人心者也。不可以主合言者而废单言也。亦不可主其单言而废其合言也。或单或合。宜随所当而言之。今以合理气言者。为晚年定论。则单指气言者。其可以非定论而弃之耶。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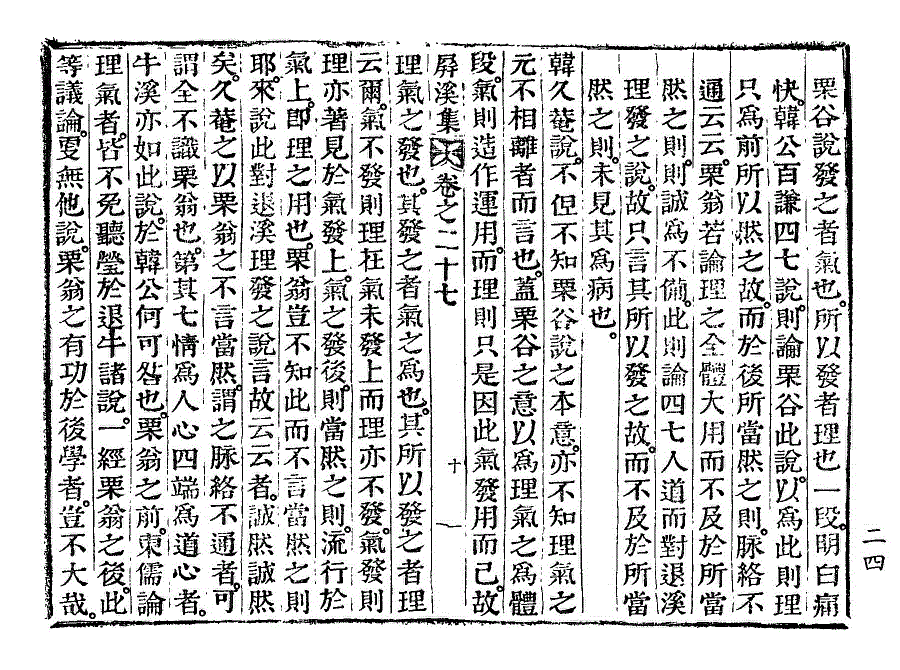 栗谷说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一段。明白痛快。韩公百谦四七说。则论栗谷此说。以为此则理只为前所以然之故。而于后所当然之则。脉络不通云云。栗翁若论理之全体大用而不及于所当然之则。则诚为不备。此则论四七人道而对退溪理发之说。故只言其所以发之故。而不及于所当然之则。未见其为病也。
栗谷说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一段。明白痛快。韩公百谦四七说。则论栗谷此说。以为此则理只为前所以然之故。而于后所当然之则。脉络不通云云。栗翁若论理之全体大用而不及于所当然之则。则诚为不备。此则论四七人道而对退溪理发之说。故只言其所以发之故。而不及于所当然之则。未见其为病也。韩久庵说。不但不知栗谷说之本意。亦不知理气之元不相离者而言也。盖栗谷之意以为理气之为体段。气则造作运用。而理则只是因此气发用而已。故理气之发也。其发之者气之为也。其所以发之者理云尔。气不发则理在气未发上而理亦不发。气发则理亦著见于气发上。气之发后。则当然之则。流行于气上。即理之用也。栗翁岂不知此而不言当然之则耶。来说此对退溪理发之说言故云云者。诚然诚然矣。久庵之以栗翁之不言当然。谓之脉络不通者。可谓全不识栗翁也。第其七情为人心四端为道心者。牛溪亦如此说。于韩公何可咎也。栗翁之前。东儒论理气者。皆不免听莹于退,牛诸说。一经栗翁之后。此等议论。更无他说。栗翁之有功于后学者。岂不大哉。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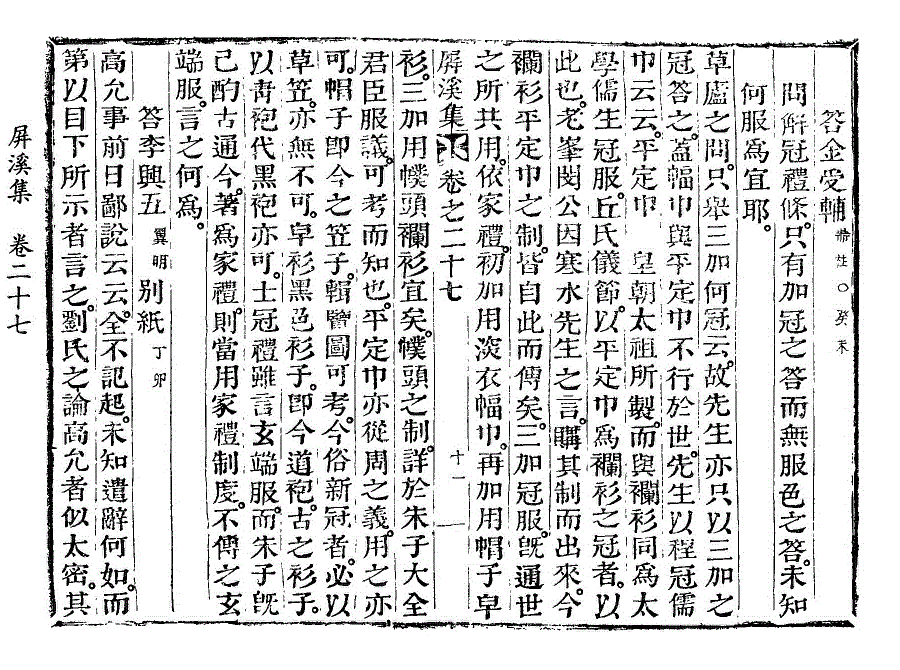 答金受辅(鼎柱○癸未)
答金受辅(鼎柱○癸未)问解冠礼条。只有加冠之答而无服色之答。未知何服为宜耶。
草庐之问。只举三加何冠云。故先生亦只以三加之冠答之。盖幅巾与平定巾不行于世。先生以程冠儒巾云云。平定巾 皇朝太祖所制。而与襕衫同为太学儒生冠服。丘氏仪节。以平定巾为襕衫之冠者。以此也。老峰闵公因寒水先生之言。购其制而出来。今襕衫平定巾之制。皆自此而传矣。三加冠服。既通世之所共用。依家礼。初加用深衣幅巾。再加用帽子皂衫。三加用幞头襕衫宜矣。幞头之制。详于朱子大全君臣服议。可考而知也。平定巾亦从周之义。用之亦可。帽子即今之笠子。辑览图可考。今俗新冠者。必以草笠。亦无不可。皂衫黑色衫子。即今道袍。古之衫子。以青袍代黑袍亦可。士冠礼虽言玄端服。而朱子既已酌古通今。著为家礼。则当用家礼制度。不传之玄端服。言之何为。
答李兴五(翼明)别纸(丁卯)
高允事前日鄙说云云。全不记起。未知遣辞何如。而第以目下所示者言之。刘氏之论高允者似太密。其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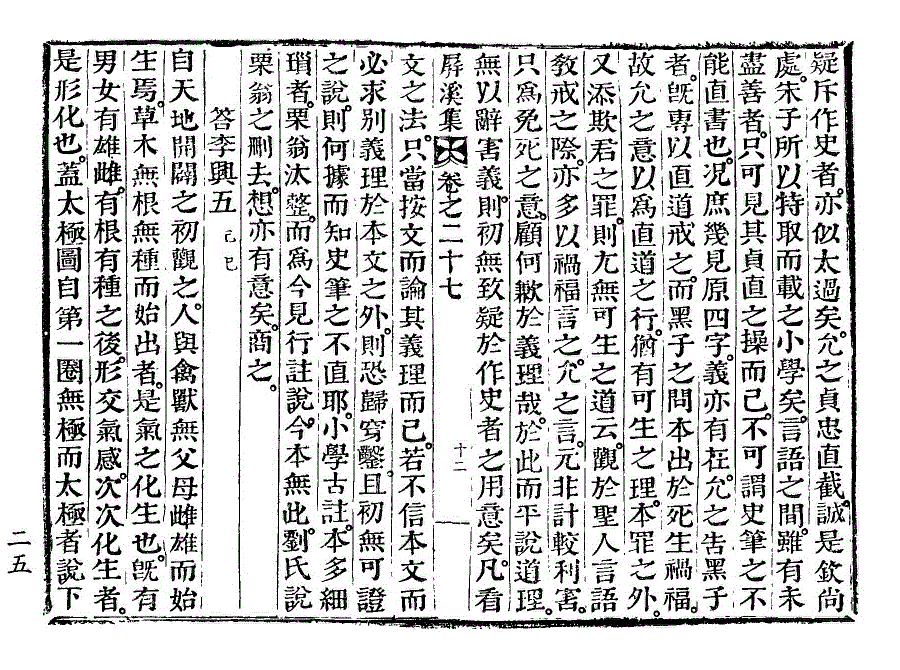 疑斥作史者。亦似太过矣。允之贞忠直截。诚是钦尚处。朱子所以特取而载之小学矣。言语之间。虽有未尽善者。只可见其贞直之操而已。不可谓史笔之不能直书也。况庶几见原四字。义亦有在。允之告黑子者。既专以直道戒之。而黑子之问本出于死生祸福。故允之意以为直道之行。犹有可生之理。本罪之外。又添欺君之罪。则尤无可生之道云。观于圣人言语教戒之际。亦多以祸福言之。允之言。元非计较利害。只为免死之意。顾何歉于义理哉。于此而平说道理。无以辞害义。则初无致疑于作史者之用意矣。凡看文之法。只当按文而论其义理而已。若不信本文而必求别义理于本文之外。则恐归穿凿。且初无可證之说。则何据而知史笔之不直耶。小学古注。本多细琐者。栗翁汰整。而为今见行注说。今本无此。刘氏说栗翁之删去。想亦有意矣。商之。
疑斥作史者。亦似太过矣。允之贞忠直截。诚是钦尚处。朱子所以特取而载之小学矣。言语之间。虽有未尽善者。只可见其贞直之操而已。不可谓史笔之不能直书也。况庶几见原四字。义亦有在。允之告黑子者。既专以直道戒之。而黑子之问本出于死生祸福。故允之意以为直道之行。犹有可生之理。本罪之外。又添欺君之罪。则尤无可生之道云。观于圣人言语教戒之际。亦多以祸福言之。允之言。元非计较利害。只为免死之意。顾何歉于义理哉。于此而平说道理。无以辞害义。则初无致疑于作史者之用意矣。凡看文之法。只当按文而论其义理而已。若不信本文而必求别义理于本文之外。则恐归穿凿。且初无可證之说。则何据而知史笔之不直耶。小学古注。本多细琐者。栗翁汰整。而为今见行注说。今本无此。刘氏说栗翁之删去。想亦有意矣。商之。答李兴五(己巳)
自天地开辟之初观之。人与禽兽无父母雌雄而始生焉。草木无根无种而始出者。是气之化生也。既有男女有雄雌。有根有种之后。形交气感。次次化生者。是形化也。盖太极图自第一圈无极而太极者说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6H 页
 来。则次次说阳动阴静五行之生。以至气化形化者。实从开辟初言之也。朱子注说外。不可以他说解之矣。然形交以后亦莫非气感而化之也。所示程朱徐黄等说。未知必与图说注牴牾也。更商之。
来。则次次说阳动阴静五行之生。以至气化形化者。实从开辟初言之也。朱子注说外。不可以他说解之矣。然形交以后亦莫非气感而化之也。所示程朱徐黄等说。未知必与图说注牴牾也。更商之。健顺五常。物亦有焉。虎仁蜂义。先儒已言。而又其同类相爱。子母相亲是仁。避凶趋吉。依主背人是义。得食相让是礼。鸣必应时是智。推之他物。莫不皆然。则亦见其全不见其偏也。虽然。人性与物性大有不相同者。物之仁义礼智。仅各明一二路而已。其推去不通处。终不得通。若人则仁极其全体。自亲亲长长而推及于一草一木。义极其全体。自敬亲敬长而推及于至微至细。礼智亦然。故人之与物。不啻悬绝也。人极其全物。极其偏人。极其通物。极其塞未知如何。
此辨人物性偏全之说而极明快矣。第彼主人物性同之说者。非不知此。而每曰惟此偏全。因气之有偏全。故性亦有偏全也。此所以谓气质之性也。若本然之性则只指元初所赋之理之同者。谓之人物之性所同也。盖不知性字之义而然也。性即理也者。实就形气上单指所赋之理而言也。以其理之各具于形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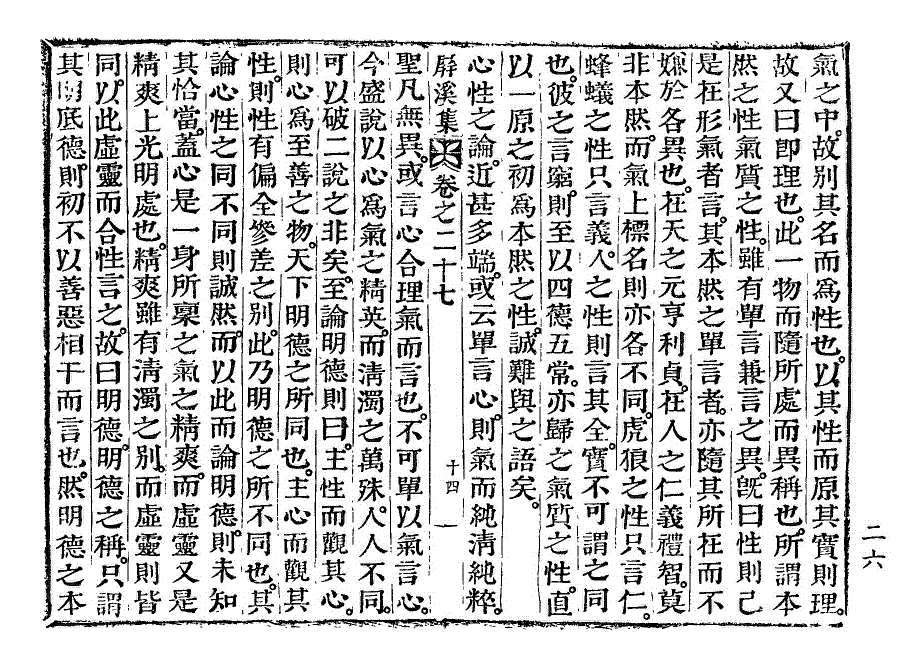 气之中。故别其名而为性也。以其性而原其实则理。故又曰即理也。此一物而随所处而异称也。所谓本然之性气质之性。虽有单言兼言之异。既曰性则已是在形气者言。其本然之单言者。亦随其所在而不嫌于各异也。在天之元亨利贞。在人之仁义礼智。莫非本然。而气上标名则亦各不同。虎狼之性只言仁。蜂蚁之性只言义。人之性则言其全。实不可谓之同也。彼之言穷。则至以四德五常。亦归之气质之性。直以一原之初为本然之性。诚难与之语矣。
气之中。故别其名而为性也。以其性而原其实则理。故又曰即理也。此一物而随所处而异称也。所谓本然之性气质之性。虽有单言兼言之异。既曰性则已是在形气者言。其本然之单言者。亦随其所在而不嫌于各异也。在天之元亨利贞。在人之仁义礼智。莫非本然。而气上标名则亦各不同。虎狼之性只言仁。蜂蚁之性只言义。人之性则言其全。实不可谓之同也。彼之言穷。则至以四德五常。亦归之气质之性。直以一原之初为本然之性。诚难与之语矣。心性之论。近甚多端。或云单言心。则气而纯清纯粹。圣凡无异。或言心合理气而言也。不可单以气言心。今盛说以心为气之精英。而清浊之万殊。人人不同。可以破二说之非矣。至论明德则曰。主性而观其心。则心为至善之物。天下明德之所同也。主心而观其性。则性有偏全参差之别。此乃明德之所不同也。其论心性之同不同则诚然。而以此而论明德。则未知其恰当。盖心是一身所禀之气之精爽。而虚灵又是精爽上光明处也。精爽虽有清浊之别。而虚灵则皆同。以此虚灵而合性言之。故曰明德。明德之称。只谓其明底德。则初不以善恶相干而言也。然明德之本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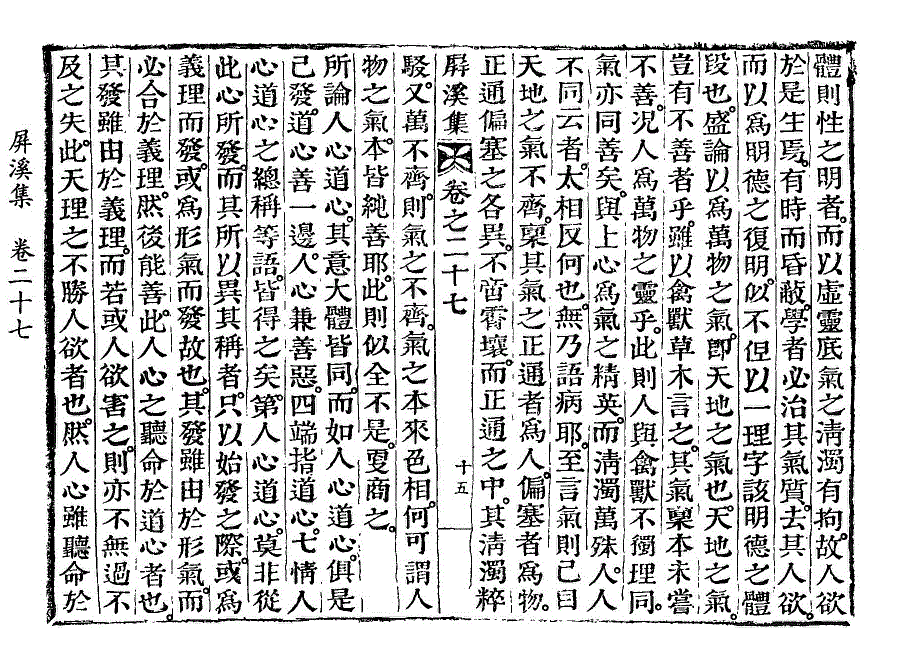 体则性之明者。而以虚灵底气之清浊有拘。故人欲于是生焉。有时而昏蔽。学者必治其气质。去其人欲。而以为明德之复明。似不但以一理字该明德之体段也。盛论以为万物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天地之气。岂有不善者乎。虽以禽兽草木言之。其气禀本未尝不善。况人为万物之灵乎。此则人与禽兽不独理同。气亦同善矣。与上心为气之精英。而清浊万殊。人人不同云者。太相反何也。无乃语病耶。至言气则已自天地之气不齐。禀其气之正通者为人。偏塞者为物。正通偏塞之各异。不啻霄壤。而正通之中。其清浊粹驳。又万不齐。则气之不齐。气之本来色相。何可谓人物之气。本皆纯善耶。此则似全不是。更商之。
体则性之明者。而以虚灵底气之清浊有拘。故人欲于是生焉。有时而昏蔽。学者必治其气质。去其人欲。而以为明德之复明。似不但以一理字该明德之体段也。盛论以为万物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天地之气。岂有不善者乎。虽以禽兽草木言之。其气禀本未尝不善。况人为万物之灵乎。此则人与禽兽不独理同。气亦同善矣。与上心为气之精英。而清浊万殊。人人不同云者。太相反何也。无乃语病耶。至言气则已自天地之气不齐。禀其气之正通者为人。偏塞者为物。正通偏塞之各异。不啻霄壤。而正通之中。其清浊粹驳。又万不齐。则气之不齐。气之本来色相。何可谓人物之气。本皆纯善耶。此则似全不是。更商之。所论人心道心。其意大体皆同。而如人心道心。俱是已发。道心善一边。人心兼善恶。四端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总称等语。皆得之矣。第人心道心。莫非从此心所发。而其所以异其称者。只以始发之际。或为义理而发。或为形气而发故也。其发虽由于形气。而必合于义理。然后能善。此人心之听命于道心者也。其发虽由于义理。而若或人欲害之。则亦不无过不及之失。此天理之不胜人欲者也。然人心虽听命于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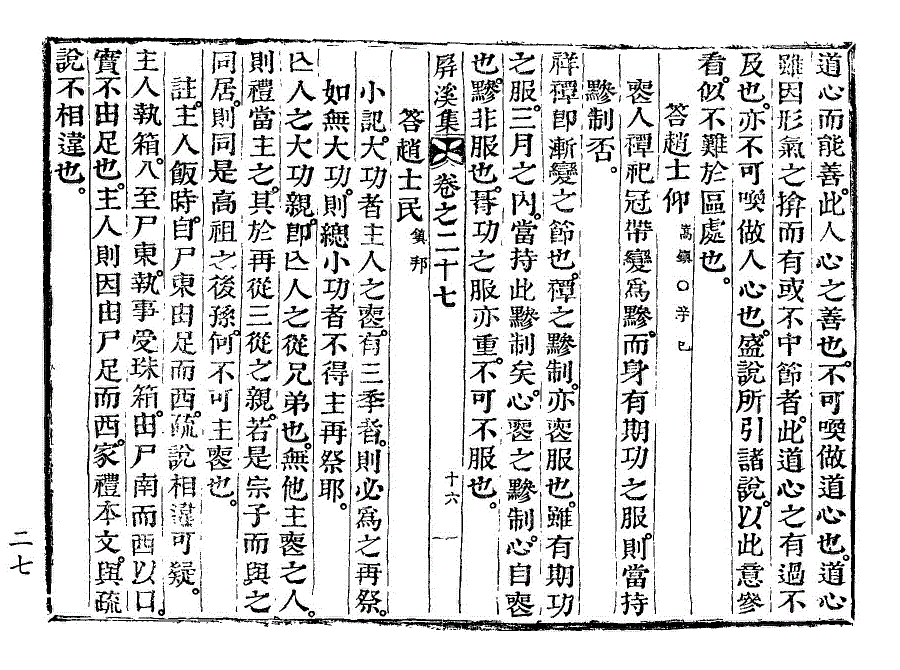 道心而能善。此人心之善也。不可唤做道心也。道心虽因形气之掩而有或不中节者。此道心之有过不及也。亦不可唤做人心也。盛说所引诸说。以此意参看。似不难于区处也。
道心而能善。此人心之善也。不可唤做道心也。道心虽因形气之掩而有或不中节者。此道心之有过不及也。亦不可唤做人心也。盛说所引诸说。以此意参看。似不难于区处也。答赵士仰(嵩镇○辛巳)
丧人禫祀冠带变为黪。而身有期功之服。则当持黪制否。
祥禫即渐变之节也。禫之黪制。亦丧服也。虽有期功之服。三月之内。当持此黪制矣。心丧之黪制。心自丧也。黪非服也。期功之服亦重。不可不服也。
答赵士民(镇邦)
小记。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如无大功。则缌小功者不得主再祭耶。
亡人之大功亲。即亡人之从兄弟也。无他主丧之人。则礼当主之。其于再从三从之亲。若是宗子而与之同居。则同是高祖之后孙。何不可主丧也。
注。主人饭时。自尸东由足而西。疏说相违可疑。
主人执箱。入至尸东。执事受珠箱。由尸南而西以口。实不由足也。主人则因由尸足而西。家礼本文。与疏说不相违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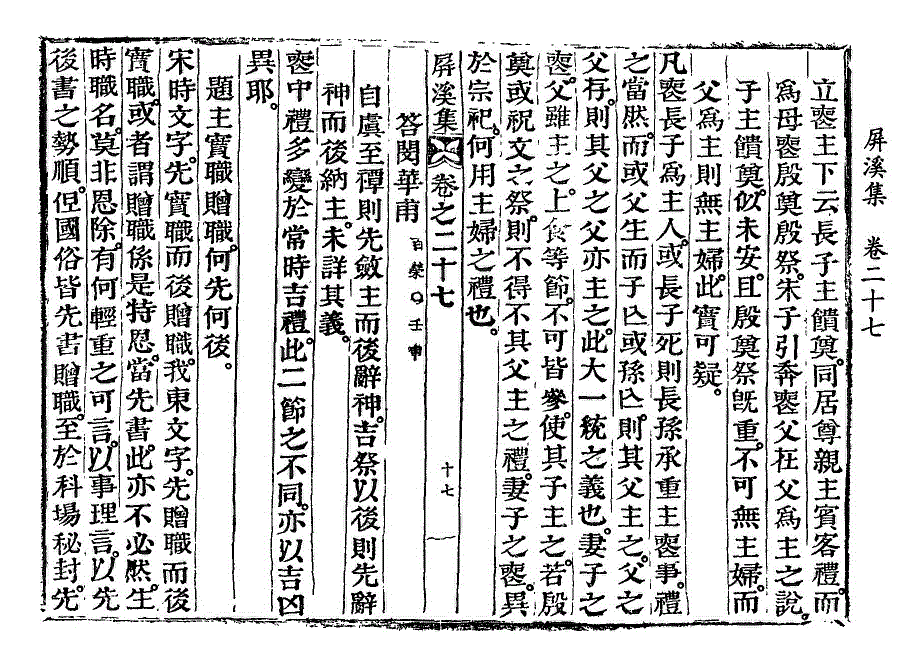 立丧主下云长子主馈奠。同居尊亲主宾客礼。而为母丧殷奠殷祭。朱子引奔丧父在父为主之说。子主馈奠。似未安。且殷奠祭既重。不可无主妇。而父为主则无主妇。此实可疑。
立丧主下云长子主馈奠。同居尊亲主宾客礼。而为母丧殷奠殷祭。朱子引奔丧父在父为主之说。子主馈奠。似未安。且殷奠祭既重。不可无主妇。而父为主则无主妇。此实可疑。凡丧长子为主人。或长子死则长孙承重主丧事。礼之当然。而或父生而子亡或孙亡。则其父主之。父之父存。则其父之父亦主之。此大一统之义也。妻子之丧。父虽主之。上食等节。不可皆参。使其子主之。若殷奠或祝文之祭。则不得不其父主之礼。妻子之丧。异于宗祀。何用主妇之礼也。
答闵华甫(百荣○壬申)
自虞至禫则先敛主而后辞神。吉祭以后则先辞神而后纳主。未详其义。
丧中礼多变于常时吉礼。此二节之不同。亦以吉凶异耶。
题主实职赠职。何先何后。
宋时文字。先实职而后赠职。我东文字。先赠职而后实职。或者谓赠职系是特恩。当先书。此亦不必然。生时职名。莫非恩除。有何轻重之可言。以事理言。以先后书之势顺。但国俗皆先书赠职。至于科场秘封。先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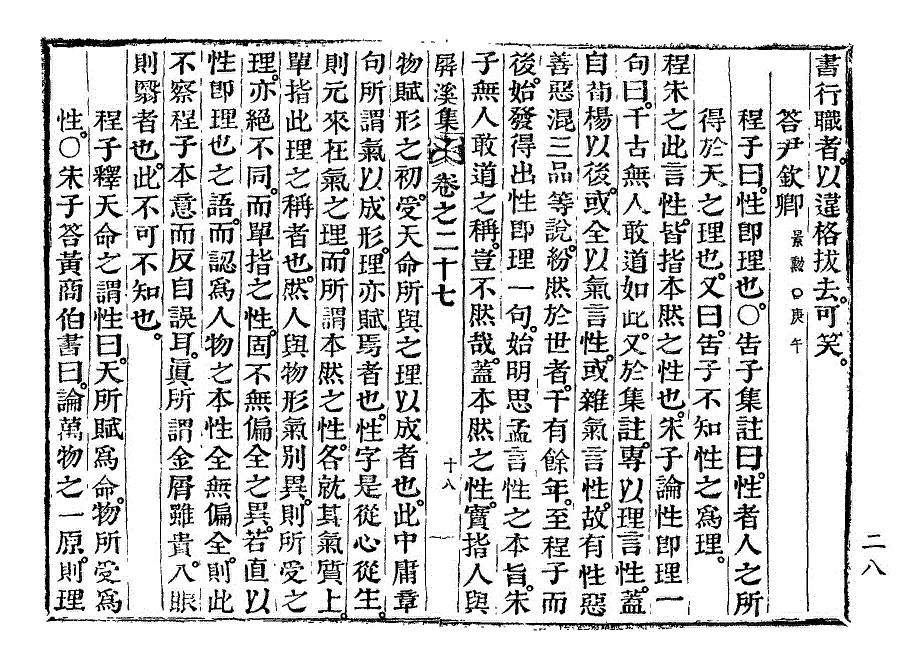 书行职者。以违格拔去。可笑。
书行职者。以违格拔去。可笑。答尹钦卿(景勋○庚午)
程子曰。性即理也。○告子集注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又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
程朱之此言性。皆指本然之性也。朱子论性即理一句曰。千古无人敢道如此。又于集注。专以理言性。盖自荀杨以后。或全以气言性。或杂气言性。故有性恶善恶混三品等说。纷然于世者。千有馀年。至程子而后。始发得出性即理一句。始明思孟言性之本旨。朱子无人敢道之称。岂不然哉。盖本然之性。实指人与物赋形之初。受天命所与之理以成者也。此中庸章句所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也。性字是从心从生。则元来在气之理。而所谓本然之性。各就其气质上。单指此理之称者也。然人与物形气别异。则所受之理。亦绝不同。而单指之性。固不无偏全之异。若直以性即理也之语。而认为人物之本性全无偏全。则此不察程子本意而反自误耳。真所谓金屑虽贵。入眼则翳者也。此不可不知也。
程子释天命之谓性曰。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朱子答黄商伯书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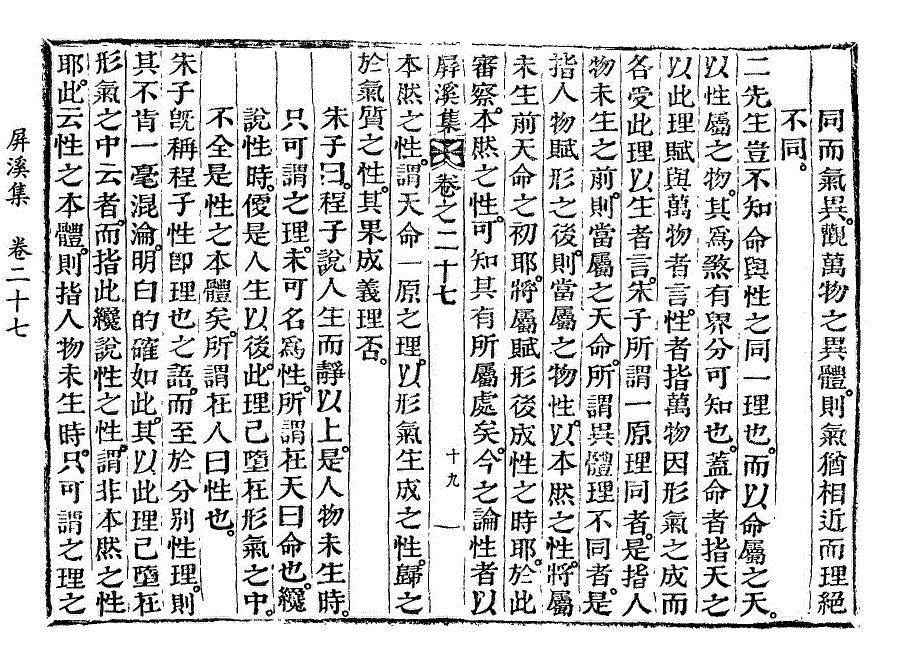 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
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二先生岂不知命与性之同一理也。而以命属之天。以性属之物。其为煞有界分可知也。盖命者指天之以此理赋与万物者言。性者指万物因形气之成而各受此理以生者言。朱子所谓一原理同者。是指人物未生之前。则当属之天命。所谓异体理不同者。是指人物赋形之后。则当属之物性。以本然之性。将属未生前天命之初耶。将属赋形后成性之时耶。于此审察。本然之性。可知其有所属处矣。今之论性者以本然之性。谓天命一原之理。以形气生成之性。归之于气质之性。其果成义理否。
朱子曰。程子说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
朱子既称程子性即理也之语。而至于分别性理。则其不肯一毫混沦。明白的确如此。其以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云者。而指此才说性之性。谓非本然之性耶。此云性之本体。则指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29L 页
 理也。先儒亦云程子此端。便已不是性之性。即指理字也。以此参看朱子说。尤分明矣。
理也。先儒亦云程子此端。便已不是性之性。即指理字也。以此参看朱子说。尤分明矣。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太极图说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中庸章句曰。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又曰。各循其性之自然。
语类。朱子又论各得所赋之理而曰。马之性健。牛之性顺。虎狼之性仁。蜂蚁之性义云云。盖言其各禀其性之意也。易以下诸说。各字皆一意也。性字皆形气上言。故虽单言其性。而其不同如此。此以其异体上言。则理绝不同者也。岂可以易彖各正之性。图说各一之性。章句各得各循之性。各自不同。而谓非本然之性耶。
明道先生曰。循性者。马则为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底性。又不做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朱子论循性之道曰。循人之性则为人之道。循牛马之性则为牛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马耕而牛驰。则失其性。非牛马之道矣。○又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不杂气禀而专言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0H 页
 以朱子便说率性之道不去之语观之。率性之性。明是本然者可知。而明道与朱子牛马之性云云。皆是说率性之道。则其言本然之性。马与牛之不同如此。人物之性不同。亦可较然矣。后人何故言本然之性。则必谓人与物之皆同也。
以朱子便说率性之道不去之语观之。率性之性。明是本然者可知。而明道与朱子牛马之性云云。皆是说率性之道。则其言本然之性。马与牛之不同如此。人物之性不同。亦可较然矣。后人何故言本然之性。则必谓人与物之皆同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大学或问曰。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孟子犬牛人三性下集注谓性者。所得于天之理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然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以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又曰。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语类曰。仁义礼智之粹然。物则无之。
或问其性最贵之语。本出于孝经。而孔子既以天地之性言之。则此性字明是本然之性。而与一原理同。对待言之。其以本然之性。与一原之理。所指之不同。明白如此。且谓人性之万物中最贵。则人物本然之性之不同亦如此。至于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则尤大䡈著。其曰性者天之理。又曰。仁义礼智云。则其言本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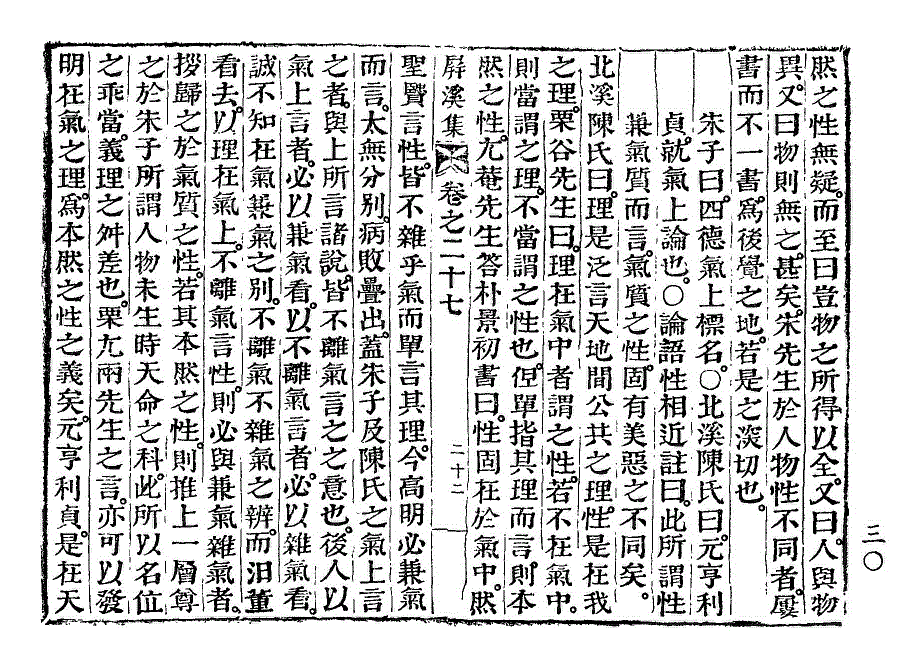 然之性无疑。而至曰岂物之所得以全。又曰。人与物异。又曰物则无之。甚矣。朱先生于人物性不同者。屡书而不一书。为后觉之地。若是之深切也。
然之性无疑。而至曰岂物之所得以全。又曰。人与物异。又曰物则无之。甚矣。朱先生于人物性不同者。屡书而不一书。为后觉之地。若是之深切也。朱子曰。四德气上标名。○北溪陈氏曰。元亨利贞。就气上论也。○论语性相近注曰。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
北溪陈氏曰。理是泛言天地间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栗谷先生曰。理在气中者谓之性。若不在气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也。但单指其理而言。则本然之性。尤庵先生答朴景初书曰。性固在于气中。然圣贤言性。皆不杂乎气而单言其理。今高明必兼气而言。太无分别。病败叠出。盖朱子及陈氏之气上言之者。与上所言诸说。皆不离气言之之意也。后人以气上言者。必以兼气看。以不离气言者。必以杂气看。诚不知在气兼气之别。不离气不杂气之辨。而汨董看去。以理在气上。不离气言性。则必与兼气杂气者。拶归之于气质之性。若其本然之性。则推上一层尊之于朱子所谓人物未生时天命之科。此所以名位之乖当。义理之舛差也。栗尤两先生之言。亦可以发明在气之理。为本然之性之义矣。元亨利贞。是在天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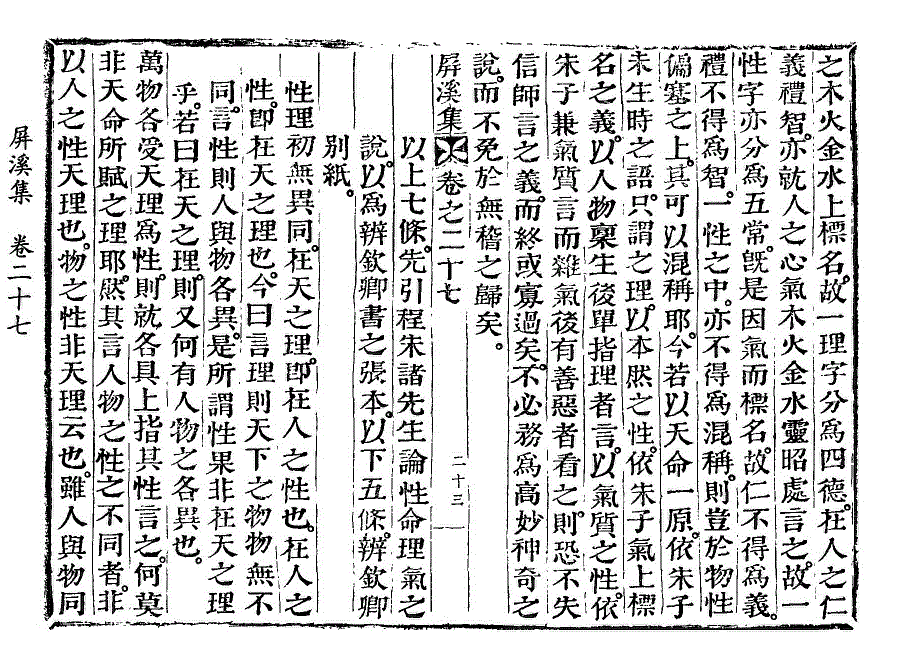 之木火金水上标名。故一理字分为四德。在人之仁义礼智。亦就人之心气木火金水灵昭处言之。故一性字亦分为五常。既是因气而标名。故仁不得为义。礼不得为智。一性之中。亦不得为混称。则岂于物性偏塞之上。其可以混称耶。今若以天命一原。依朱子未生时之语。只谓之理。以本然之性。依朱子气上标名之义。以人物禀生后单指理者言。以气质之性。依朱子兼气质言而杂气后有善恶者看之。则恐不失信师言之义。而终或寡过矣。不必务为高妙神奇之说。而不免于无稽之归矣。
之木火金水上标名。故一理字分为四德。在人之仁义礼智。亦就人之心气木火金水灵昭处言之。故一性字亦分为五常。既是因气而标名。故仁不得为义。礼不得为智。一性之中。亦不得为混称。则岂于物性偏塞之上。其可以混称耶。今若以天命一原。依朱子未生时之语。只谓之理。以本然之性。依朱子气上标名之义。以人物禀生后单指理者言。以气质之性。依朱子兼气质言而杂气后有善恶者看之。则恐不失信师言之义。而终或寡过矣。不必务为高妙神奇之说。而不免于无稽之归矣。以上七条。先引程朱诸先生论性命理气之说。以为辨钦卿书之张本。以下五条。辨钦卿别纸。
性理初无异同。在天之理。即在人之性也。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今曰言理则天下之物物无不同。言性则人与物各异。是所谓性果非在天之理乎。若曰在天之理。则又何有人物之各异也。
万物各受天理为性。则就各具上指其性言之。何莫非天命所赋之理耶。然其言人物之性之不同者。非以人之性天理也。物之性非天理云也。虽人与物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1L 页
 受天理为性。而以气之偏全而性亦有偏全云耳。朱子答徐子融书曰。惟人心最灵。故能全此四德。物则气偏驳。固有所不能全。又答余方叔书曰。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方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一般。勉斋曰。仁义礼智。特因人心而立名。以上所證程朱诸说。已多人物性偏全之不同者。而今以朱子勉斋说见之。其偏全之不同。一言可辨。何必尽弃程朱诸说而胶固于旧见耶。性非不是理。而因气而标名。故不能不异。不必以万物之性汗漫言之也。只以健顺五常言之。亦可见矣。阳之性健。阴之性顺。木之性仁。金之性义。而健与顺不同。仁与义不同者。以其气之各异故也。亦岂以健顺仁义之各异其称。而谓非本然之性耶。犬牛人之气。既绝不同。故以其所受而言之。理亦绝不同。正朱子所谓异体之理。绝不同也。于此打破。则许多异同之论。不难辨矣。
受天理为性。而以气之偏全而性亦有偏全云耳。朱子答徐子融书曰。惟人心最灵。故能全此四德。物则气偏驳。固有所不能全。又答余方叔书曰。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方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一般。勉斋曰。仁义礼智。特因人心而立名。以上所證程朱诸说。已多人物性偏全之不同者。而今以朱子勉斋说见之。其偏全之不同。一言可辨。何必尽弃程朱诸说而胶固于旧见耶。性非不是理。而因气而标名。故不能不异。不必以万物之性汗漫言之也。只以健顺五常言之。亦可见矣。阳之性健。阴之性顺。木之性仁。金之性义。而健与顺不同。仁与义不同者。以其气之各异故也。亦岂以健顺仁义之各异其称。而谓非本然之性耶。犬牛人之气。既绝不同。故以其所受而言之。理亦绝不同。正朱子所谓异体之理。绝不同也。于此打破。则许多异同之论。不难辨矣。下教以天地公共者谓之理。以物物各得于形气者谓之性。人之性果得于形气者耶。性有本然气质之异。本然者专主理言也。气质者兼理与气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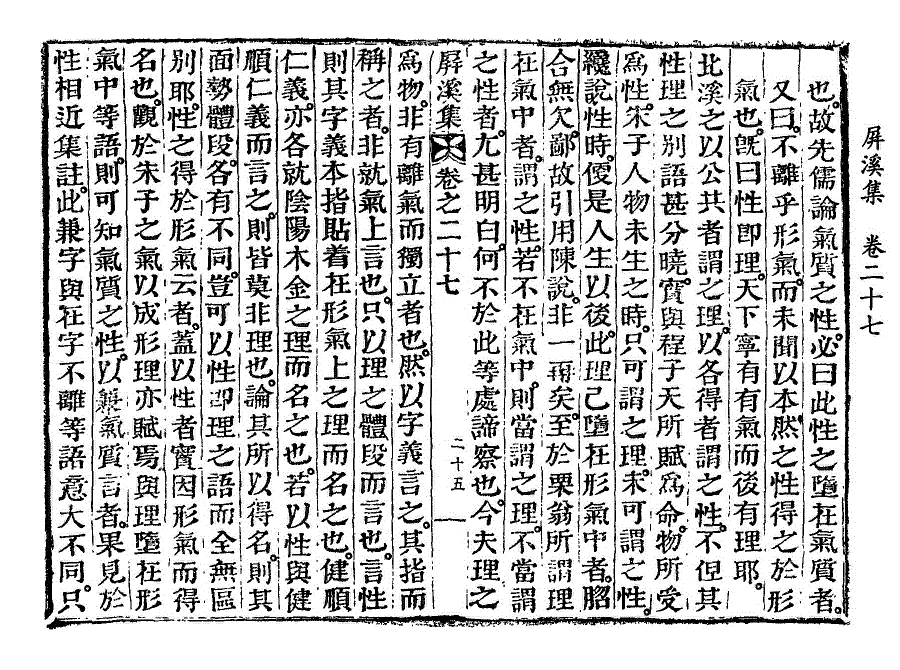 也。故先儒论气质之性。必曰此性之堕在气质者。又曰。不离乎形气。而未闻以本然之性得之于形气也。既曰性即理。天下宁有有气而后有理耶。
也。故先儒论气质之性。必曰此性之堕在气质者。又曰。不离乎形气。而未闻以本然之性得之于形气也。既曰性即理。天下宁有有气而后有理耶。北溪之以公共者谓之理。以各得者谓之性。不但其性理之别语甚分晓。实与程子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朱子人物未生之时。只可谓之理。未可谓之性。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中者。吻合无欠。鄙故引用陈说。非一再矣。至于栗翁所谓理在气中者。谓之性。若不在气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者。尤甚明白。何不于此等处谛察也。今夫理之为物。非有离气而独立者也。然以字义言之。其指而称之者。非就气上言也。只以理之体段而言也。言性则其字义本指贴着在形气上之理而名之也。健顺仁义。亦各就阴阳木金之理而名之也。若以性与健顺仁义而言之。则皆莫非理也。论其所以得名。则其面势体段。各有不同。岂可以性即理之语而全无区别耶。性之得于形气云者。盖以性者实因形气而得名也。观于朱子之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与理堕在形气中等语。则可知气质之性。以兼气质言者。果见于性相近集注。此兼字与在字不离等语意大不同。只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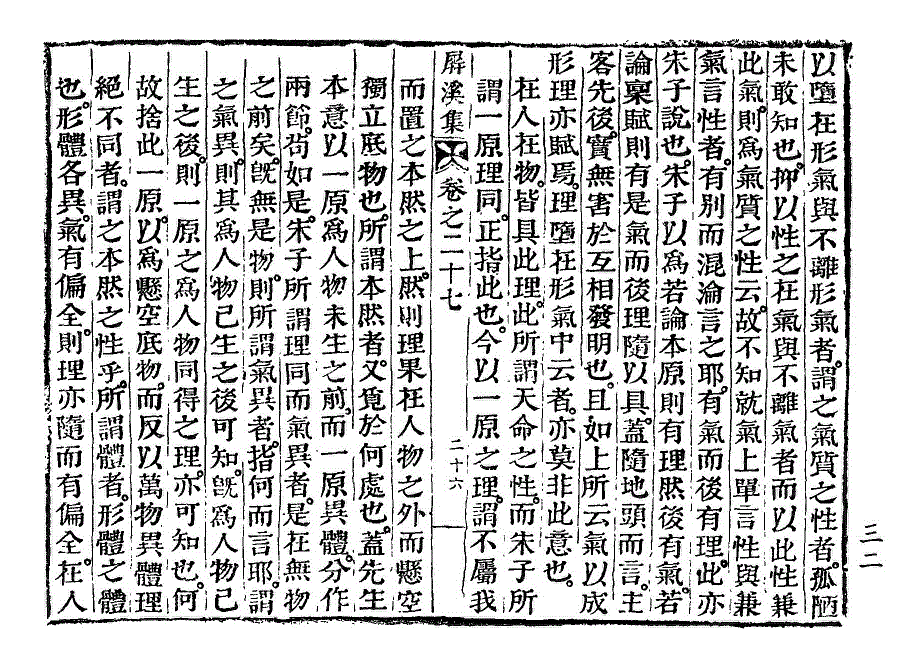 以堕在形气与不离形气者。谓之气质之性者。孤陋未敢知也。抑以性之在气与不离气者而以此性兼此气。则为气质之性云。故不知就气上单言性与兼气言性者。有别而混沦言之耶。有气而后有理。此亦朱子说也。朱子以为若论本原则有理然后有气。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盖随地头而言。主客先后。实无害于互相发明也。且如上所云气以成形理亦赋焉。理堕在形气中云者。亦莫非此意也。
以堕在形气与不离形气者。谓之气质之性者。孤陋未敢知也。抑以性之在气与不离气者而以此性兼此气。则为气质之性云。故不知就气上单言性与兼气言性者。有别而混沦言之耶。有气而后有理。此亦朱子说也。朱子以为若论本原则有理然后有气。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盖随地头而言。主客先后。实无害于互相发明也。且如上所云气以成形理亦赋焉。理堕在形气中云者。亦莫非此意也。在人在物。皆具此理。此所谓天命之性。而朱子所谓一原理同。正指此也。今以一原之理。谓不属我而置之本然之上。然则理果在人物之外而悬空独立底物也。所谓本然者。又觅于何处也。盖先生本意以一原为人物未生之前。而一原异体。分作两节。苟如是。朱子所谓理同而气异者。是在无物之前矣。既无是物。则所谓气异者。指何而言耶。谓之气异。则其为人物已生之后可知。既为人物已生之后。则一原之为人物同得之理。亦可知也。何故舍此一原。以为悬空底物。而反以万物异体理绝不同者。谓之本然之性乎。所谓体者。形体之体也。形体各异。气有偏全。则理亦随而有偏全。在人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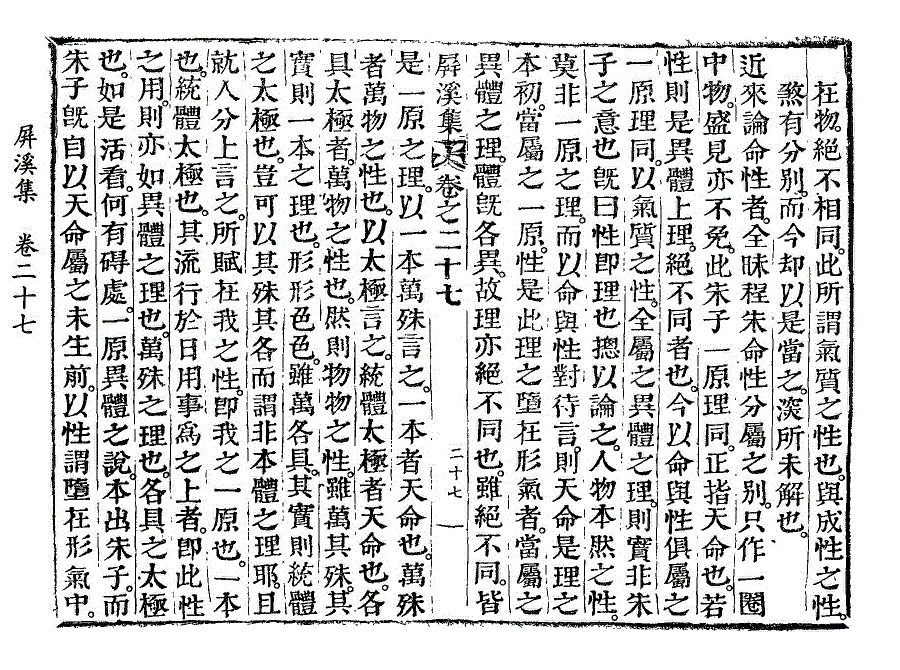 在物。绝不相同。此所谓气质之性也。与成性之性。煞有分别。而今却以是当之。深所未解也。
在物。绝不相同。此所谓气质之性也。与成性之性。煞有分别。而今却以是当之。深所未解也。近来论命性者。全昧程朱命性分属之别。只作一圈中物。盛见亦不免。此朱子一原理同。正指天命也。若性则是异体上理。绝不同者也。今以命与性俱属之一原理同。以气质之性。全属之异体之理。则实非朱子之意也既曰性即理也总以论之。人物本然之性。莫非一原之理。而以命与性对待言。则天命是理之本初。当属之一原。性是此理之堕在形气者。当属之异体之理。体既各异。故理亦绝不同也。虽绝不同。皆是一原之理。以一本万殊言之。一本者天命也。万殊者万物之性也。以太极言之。统体太极者天命也。各具太极者。万物之性也。然则物物之性。虽万其殊。其实则一本之理也。形形色色。虽万各具。其实则统体之太极也。岂可以其殊其各而谓非本体之理耶。且就人分上言之。所赋在我之性。即我之一原也。一本也。统体太极也。其流行于日用事为之上者。即此性之用。则亦如异体之理也。万殊之理也。各具之太极也。如是活看。何有碍处。一原异体之说。本出朱子。而朱子既自以天命属之未生前。以性谓堕在形气中。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3L 页
 则是属之异体之理也。后人何敢不分两节看也。理同气异者。直从理气原本。只指理则同。而气则异之体段。以为理之体段如此。气之体段如此而已云也。如以物之先后离气悬空等语为疑。则殊非立言之本意也。且以异体之理。为气质之性者。见于何书。若非朱子之说。而出于左右手分则不敢信也。成性之性。各正性命之性。各循其性之性。皆人物异体上。各受天理而为性者。而单指其理也。同一本然之性。非有所分别也。
则是属之异体之理也。后人何敢不分两节看也。理同气异者。直从理气原本。只指理则同。而气则异之体段。以为理之体段如此。气之体段如此而已云也。如以物之先后离气悬空等语为疑。则殊非立言之本意也。且以异体之理。为气质之性者。见于何书。若非朱子之说。而出于左右手分则不敢信也。成性之性。各正性命之性。各循其性之性。皆人物异体上。各受天理而为性者。而单指其理也。同一本然之性。非有所分别也。且既曰性字气上标名。又曰。此本非兼气言。性之本然。只是浑然一理。不可带气而言亦明矣。而今以为气上标名。则是不离于气也。既不离于气。而又谓之非兼气言者何也。
此亦在气兼气二者。不能分看之故也。今言理者泛说也。性者理之堕在形气中言也。此正栗谷所谓若不在气。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者也。若本然之性云者。就形气上单言其理之称也。气质之性者。兼此气质而有善恶之称也。今并与在气者而同归之于兼气质之性。先贤许多论性者。其将一扫而弃之耶。元亨利贞之理。同一理也。而理之在春木上则标名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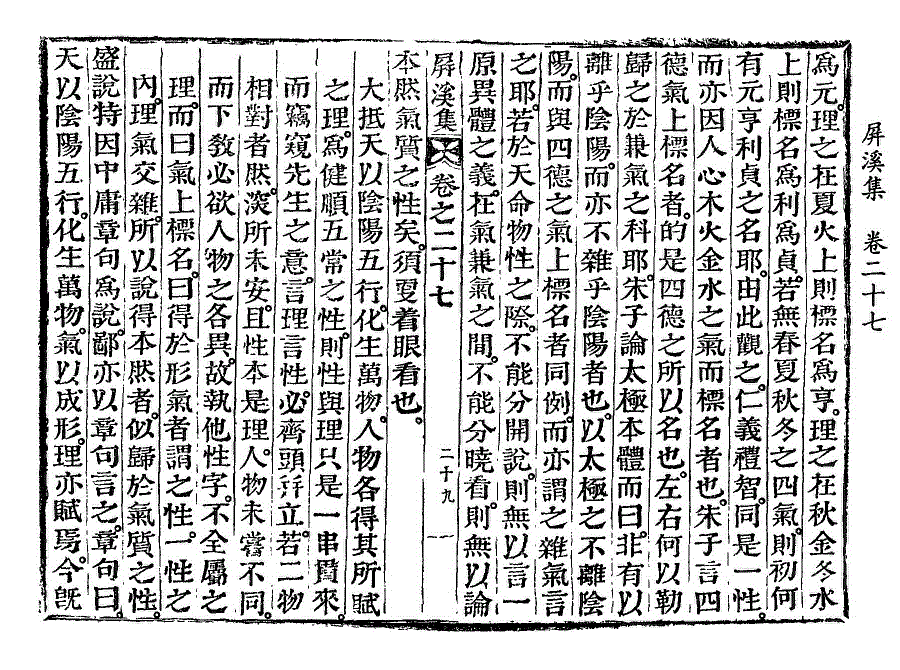 为元。理之在夏火上则标名为亨。理之在秋金冬水上则标名为利为贞。若无春夏秋冬之四气。则初何有元亨利贞之名耶。由此观之。仁义礼智。同是一性。而亦因人心木火金水之气而标名者也。朱子言四德气上标名者。的是四德之所以名也。左右何以勒归之于兼气之科耶。朱子论太极本体而曰。非有以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者也。以太极之不离阴阳。而与四德之气上标名者同例。而亦谓之杂气言之耶。若于天命物性之际。不能分开说。则无以言一原异体之义。在气兼气之间。不能分晓看。则无以论本然气质之性矣。须更着眼看也。
为元。理之在夏火上则标名为亨。理之在秋金冬水上则标名为利为贞。若无春夏秋冬之四气。则初何有元亨利贞之名耶。由此观之。仁义礼智。同是一性。而亦因人心木火金水之气而标名者也。朱子言四德气上标名者。的是四德之所以名也。左右何以勒归之于兼气之科耶。朱子论太极本体而曰。非有以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者也。以太极之不离阴阳。而与四德之气上标名者同例。而亦谓之杂气言之耶。若于天命物性之际。不能分开说。则无以言一原异体之义。在气兼气之间。不能分晓看。则无以论本然气质之性矣。须更着眼看也。大抵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物各得其所赋之理。为健顺五常之性。则性与理只是一串贯来。而窃窥先生之意。言理言性。必齐头并立。若二物相对者然。深所未安。且性本是理。人物未尝不同。而下教必欲人物之各异。故执他性字。不全属之理。而曰气上标名。曰得于形气者谓之性。一性之内。理气交杂。所以说得本然者。似归于气质之性。
盛说特因中庸章句为说。鄙亦以章句言之。章句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今既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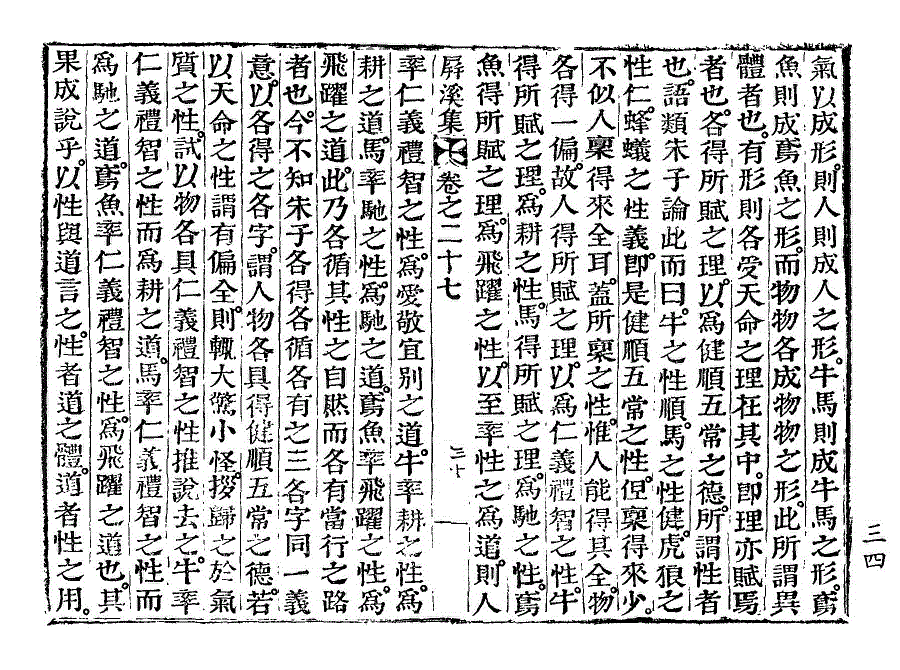 气以成形。则人则成人之形。牛马则成牛马之形。鸢鱼则成鸢鱼之形。而物物各成物物之形。此所谓异体者也。有形则各受天命之理在其中。即理亦赋焉者也。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者也。语类朱子论此而曰。牛之性顺。马之性健。虎狼之性仁。蜂蚁之性义。即是健顺五常之性。但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盖所禀之性。惟人能得其全。物各得一偏。故人得所赋之理。以为仁义礼智之性。牛得所赋之理。为耕之性。马得所赋之理。为驰之性。鸢鱼得所赋之理。为飞跃之性。以至率性之为道。则人率仁义礼智之性。为爱敬宜别之道。牛率耕之性。为耕之道。马率驰之性。为驰之道。鸢鱼率飞跃之性。为飞跃之道。此乃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当行之路者也。今不知朱子各得各循各有之三各字同一义意。以各得之各字。谓人物各具得健顺五常之德。若以天命之性谓有偏全。则辄大惊小怪。拶归之于气质之性。试以物各具仁义礼智之性推说去之。牛率仁义礼智之性而为耕之道。马率仁义礼智之性而为驰之道。鸢鱼率仁义礼智之性。为飞跃之道也。其果成说乎。以性与道言之。性者道之体。道者性之用。
气以成形。则人则成人之形。牛马则成牛马之形。鸢鱼则成鸢鱼之形。而物物各成物物之形。此所谓异体者也。有形则各受天命之理在其中。即理亦赋焉者也。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者也。语类朱子论此而曰。牛之性顺。马之性健。虎狼之性仁。蜂蚁之性义。即是健顺五常之性。但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盖所禀之性。惟人能得其全。物各得一偏。故人得所赋之理。以为仁义礼智之性。牛得所赋之理。为耕之性。马得所赋之理。为驰之性。鸢鱼得所赋之理。为飞跃之性。以至率性之为道。则人率仁义礼智之性。为爱敬宜别之道。牛率耕之性。为耕之道。马率驰之性。为驰之道。鸢鱼率飞跃之性。为飞跃之道。此乃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当行之路者也。今不知朱子各得各循各有之三各字同一义意。以各得之各字。谓人物各具得健顺五常之德。若以天命之性谓有偏全。则辄大惊小怪。拶归之于气质之性。试以物各具仁义礼智之性推说去之。牛率仁义礼智之性而为耕之道。马率仁义礼智之性而为驰之道。鸢鱼率仁义礼智之性。为飞跃之道也。其果成说乎。以性与道言之。性者道之体。道者性之用。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5H 页
 今性不能该其道。道不能循其性。亦可谓成道理否。以鄙说谓性理之齐头并立。若二物相对者然。未知何语为齐头并立。何语为二物相对耶。未可知也。且谓鄙说以性字不全属理。此全非实状。鄙说每引性即理一句语。以本然之性。谓心气上单言之理也。仁义礼智。谓心气之木火金水上标名之理也。皆得于孔子各正性命之意而以及于程朱诸说。不敢以一毫自己私见参错其间。以犯不韪之罪矣。若以性字不涉于心气。则一理字足矣。何必别称为性也。仁义礼智。不就木火金水上标名。则一性字足矣。何必以仁义礼智多少名称也。以气上之单言理者。谓之理气之交杂者。恐看文字不审。幸更另着眼也。
今性不能该其道。道不能循其性。亦可谓成道理否。以鄙说谓性理之齐头并立。若二物相对者然。未知何语为齐头并立。何语为二物相对耶。未可知也。且谓鄙说以性字不全属理。此全非实状。鄙说每引性即理一句语。以本然之性。谓心气上单言之理也。仁义礼智。谓心气之木火金水上标名之理也。皆得于孔子各正性命之意而以及于程朱诸说。不敢以一毫自己私见参错其间。以犯不韪之罪矣。若以性字不涉于心气。则一理字足矣。何必别称为性也。仁义礼智。不就木火金水上标名。则一性字足矣。何必以仁义礼智多少名称也。以气上之单言理者。谓之理气之交杂者。恐看文字不审。幸更另着眼也。答李景稷(周翼○戊辰)
示谕诸段悉之。朱子与学者论义理精微处。必戒之曰。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此言正有味。如此等义理甚微奥难见。虽或彷佛于影状。亦难明白说出。虽说得十分亭当。无反身而诚者。干我何事。况平日无体验之实。终无有真知之理耶。此不可不先讲究也。第未发已发者气也。天命之性。即其气中所赋之理也。人之生也。此气此理。一时俱禀得来。元无先后无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5L 页
 离合。但人之指而言者。或先而或后。或离而或合之也。盖必如此然后。道理明尽故也。先贤论理文字。必识其本意而看下。可无泥滞之患。不然而于先后离合之说。拘于一义。千言万语。皆欲以此律之。则将触处不通。此学者之大忌也。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思孟非不知此性之赋于气者。而子思则只言其性即天理也。孟子只言性是天理故纯善云云。直就人物禀气中。拈出所赋之性单言之。荀杨辈兼气言性者。便自脱空。而两圣为后学虑者。其功至大矣。来示真氏语。盖谓心之未发。气不用事。故此性不之喜不之怒。而浑然而已云。此正不失中庸之意也。然朱子谓喜怒哀乐未发时。所谓气质之性。亦在其中。盖此气虽未发。而非离于性而别置也。以浑然之性。合此未发之气而言。则亦气质之性也。特子思单言性。朱子合气而言。故其言异耳。究其实则义无加损矣。何必已发后。方可言气质之性耶。但性本纯善。虽发亦似无恶。而人之性发。不能无善恶之相杂。世之言性者。一是皆迷于此。多疑此性之元自不纯。为此发后善恶之种子。故程张特发挥出气质之性之名号。其意以为所禀之气。自非上圣之资。必有清浊之
离合。但人之指而言者。或先而或后。或离而或合之也。盖必如此然后。道理明尽故也。先贤论理文字。必识其本意而看下。可无泥滞之患。不然而于先后离合之说。拘于一义。千言万语。皆欲以此律之。则将触处不通。此学者之大忌也。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思孟非不知此性之赋于气者。而子思则只言其性即天理也。孟子只言性是天理故纯善云云。直就人物禀气中。拈出所赋之性单言之。荀杨辈兼气言性者。便自脱空。而两圣为后学虑者。其功至大矣。来示真氏语。盖谓心之未发。气不用事。故此性不之喜不之怒。而浑然而已云。此正不失中庸之意也。然朱子谓喜怒哀乐未发时。所谓气质之性。亦在其中。盖此气虽未发。而非离于性而别置也。以浑然之性。合此未发之气而言。则亦气质之性也。特子思单言性。朱子合气而言。故其言异耳。究其实则义无加损矣。何必已发后。方可言气质之性耶。但性本纯善。虽发亦似无恶。而人之性发。不能无善恶之相杂。世之言性者。一是皆迷于此。多疑此性之元自不纯。为此发后善恶之种子。故程张特发挥出气质之性之名号。其意以为所禀之气。自非上圣之资。必有清浊之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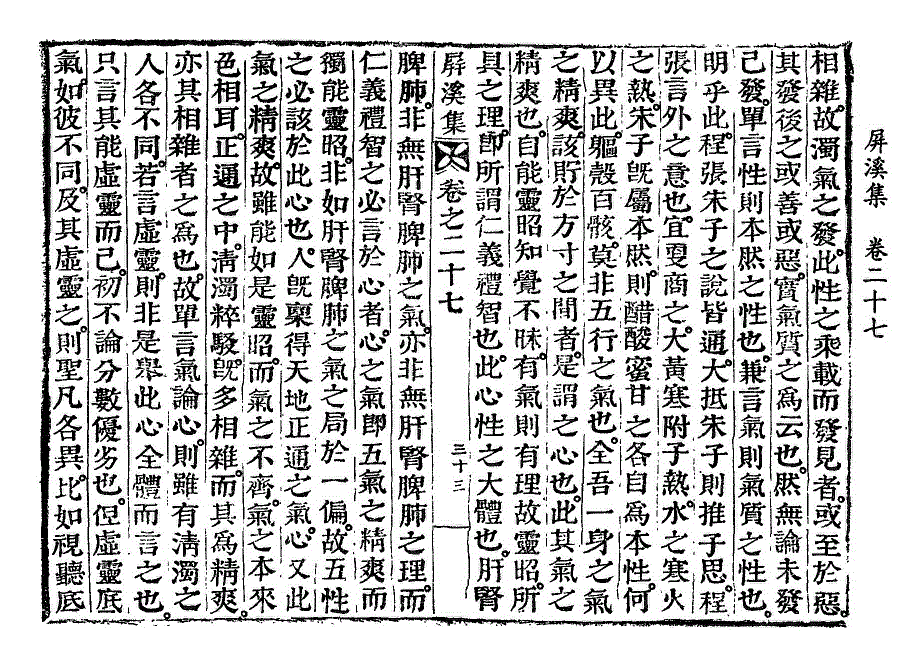 相杂。故浊气之发。此性之乘载而发见者。或至于恶。其发后之或善或恶。实气质之为云也。然无论未发已发。单言性则本然之性也。兼言气则气质之性也。明乎此。程张朱子之说皆通。大抵朱子则推子思。程张言外之意也。宜更商之。大黄寒附子热。水之寒火之热。朱子既属本然。则醋酸蜜甘之各自为本性。何以异此。躯壳百骸。莫非五行之气也。全吾一身之气之精爽。该贮于方寸之间者。是谓之心也。此其气之精爽也。自能灵昭知觉不昧。有气则有理故灵昭。所具之理。即所谓仁义礼智也。此心性之大体也。肝肾脾肺。非无肝肾脾肺之气。亦非无肝肾脾肺之理。而仁义礼智之必言于心者。心之气即五气之精爽而独能灵昭。非如肝肾脾肺之气之局于一偏。故五性之必该于此心也。人既禀得天地正通之气。心又此气之精爽。故虽能如是灵昭。而气之不齐。气之本来色相耳。正通之中。清浊粹驳。既多相杂。而其为精爽。亦其相杂者之为也。故单言气论心。则虽有清浊之人各不同。若言虚灵。则非是举此心全体而言之也。只言其能虚灵而已。初不论分数优劣也。但虚灵底气。如彼不同。及其虚灵之。则圣凡各异。比如视听底
相杂。故浊气之发。此性之乘载而发见者。或至于恶。其发后之或善或恶。实气质之为云也。然无论未发已发。单言性则本然之性也。兼言气则气质之性也。明乎此。程张朱子之说皆通。大抵朱子则推子思。程张言外之意也。宜更商之。大黄寒附子热。水之寒火之热。朱子既属本然。则醋酸蜜甘之各自为本性。何以异此。躯壳百骸。莫非五行之气也。全吾一身之气之精爽。该贮于方寸之间者。是谓之心也。此其气之精爽也。自能灵昭知觉不昧。有气则有理故灵昭。所具之理。即所谓仁义礼智也。此心性之大体也。肝肾脾肺。非无肝肾脾肺之气。亦非无肝肾脾肺之理。而仁义礼智之必言于心者。心之气即五气之精爽而独能灵昭。非如肝肾脾肺之气之局于一偏。故五性之必该于此心也。人既禀得天地正通之气。心又此气之精爽。故虽能如是灵昭。而气之不齐。气之本来色相耳。正通之中。清浊粹驳。既多相杂。而其为精爽。亦其相杂者之为也。故单言气论心。则虽有清浊之人各不同。若言虚灵。则非是举此心全体而言之也。只言其能虚灵而已。初不论分数优劣也。但虚灵底气。如彼不同。及其虚灵之。则圣凡各异。比如视听底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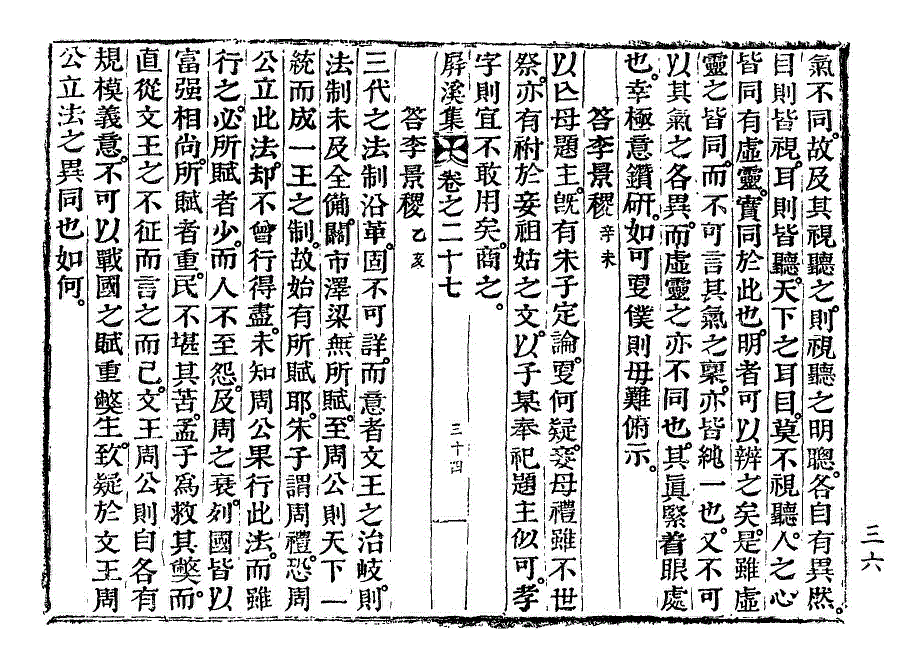 气不同。故及其视听之。则视听之明聪。各自有异然。目则皆视。耳则皆听。天下之耳目。莫不视听。人之心皆同有虚灵。实同于此也。明者可以辨之矣。是虽虚灵之皆同。而不可言其气之禀。亦皆纯一也。又不可以其气之各异。而虚灵之亦不同也。其真紧着眼处也。幸极意钻研。如可更仆则毋难俯示。
气不同。故及其视听之。则视听之明聪。各自有异然。目则皆视。耳则皆听。天下之耳目。莫不视听。人之心皆同有虚灵。实同于此也。明者可以辨之矣。是虽虚灵之皆同。而不可言其气之禀。亦皆纯一也。又不可以其气之各异。而虚灵之亦不同也。其真紧着眼处也。幸极意钻研。如可更仆则毋难俯示。答李景稷(辛未)
以亡母题主。既有朱子定论。更何疑。妾母礼虽不世祭。亦有祔于妾祖姑之文。以子某奉祀题主似可。孝字则宜不敢用矣。商之。
答李景稷(乙亥)
三代之法制沿革。固不可详。而意者文王之治岐。则法制未及全备。关市泽梁无所赋。至周公则天下一统而成一王之制。故始有所赋耶。朱子谓周礼。恐周公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未知周公果行此法。而虽行之。必所赋者少。而人不至怨。及周之衰。列国皆以富强相尚。所赋者重。民不堪其苦。孟子为救其弊。而直从文王之不征而言之而已。文王周公则自各有规模义意。不可以战国之赋重弊生。致疑于文王周公立法之异同也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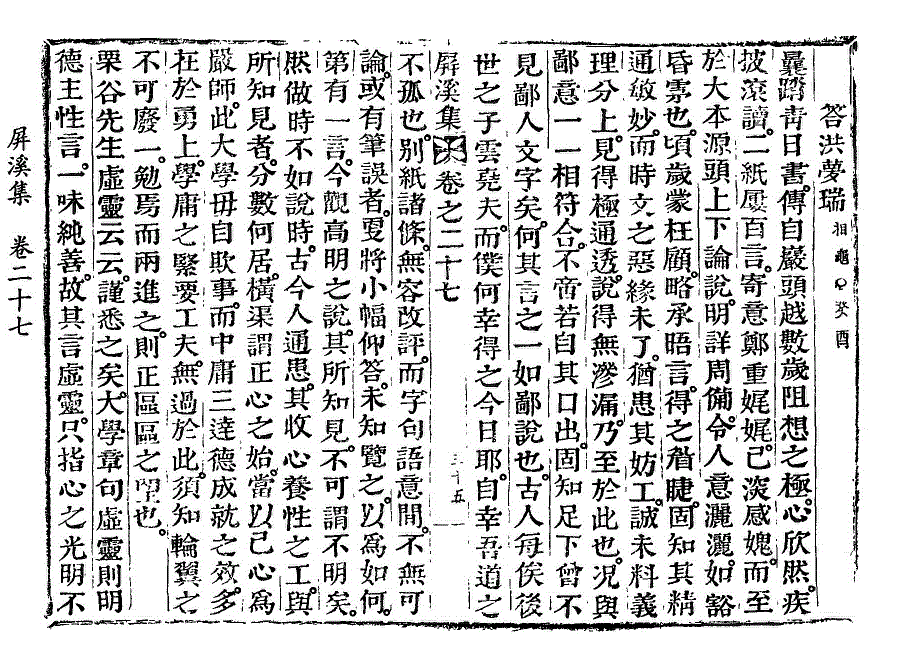 答洪梦瑞(相龟○癸酉)
答洪梦瑞(相龟○癸酉)曩踏青日书。传自岩头越数岁阻想之极。心欣然。疾披滚读。二纸屡百言。寄意郑重娓娓。已深感愧。而至于大本源头上下论说。明详周备。令人意洒洒。如豁昏雺也。顷岁蒙枉顾。略承晤言。得之眉睫。固知其精通敏妙。而时文之恶缘未了。犹患其妨工。诚未料义理分上。见得极通透。说得无渗漏。乃至于此也。况与鄙意一一相符合。不啻若自其口出。固知足下曾不见鄙人文字矣。何其言之一如鄙说也。古人每俟后世之子云尧夫。而仆何幸得之今日耶。自幸吾道之不孤也。别纸诸条。无容改评。而字句语意间。不无可论。或有笔误者。更将小幅仰答。未知览之。以为如何。第有一言。今观高明之说。其所知见。不可谓不明矣。然做时不如说时。古今人通患。其收心养性之工。与所知见者。分数何居。横渠谓正心之始。当以己心为严师。此大学毋自欺事。而中庸三达德成就之效。多在于勇上。学庸之紧要工夫。无过于此。须知轮翼之不可废一。勉焉而两进之。则正区区之望也。
栗谷先生虚灵云云。谨悉之矣。大学章句虚灵则明德主性言。一味纯善。故其言虚灵。只指心之光明不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7L 页
 昧处。以为明字张本而已。未暇说优劣。若汎言虚灵。专属气言。岂可无分数之别耶。血气含生。莫不有虚灵。而禽兽之虚灵。何可与人同。众人浊气之虚灵。与圣人清气之虚灵。亦何可同也。栗翁虚灵优劣之说。正打破释氏灵觉为性之说。十分尽到。今日心纯善之说者。正好猛省也。
昧处。以为明字张本而已。未暇说优劣。若汎言虚灵。专属气言。岂可无分数之别耶。血气含生。莫不有虚灵。而禽兽之虚灵。何可与人同。众人浊气之虚灵。与圣人清气之虚灵。亦何可同也。栗翁虚灵优劣之说。正打破释氏灵觉为性之说。十分尽到。今日心纯善之说者。正好猛省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云。则以心与仁对待说也。对待说则心以气仁以理言者。已自明白。只言三月不违。则三月之后。违于仁可知。违于仁则其气犹有渣滓之未尽化者。与夫子不踰矩之心。不能无别也。心气之不齐。在孔孟犹然。况圣凡之间乎。颜子心地不可谓血气人欲一例拘蔽。而第其所以拘蔽者。亦有浅深。其有违于仁则不可谓纯于天理也。不能纯于天理者。岂非血气人欲犹有些拘蔽而然也。其谓颜氏子有不善者。亦以此也。观于栗翁答牛溪书。论颜子一毫未尽云云者。可详。
来说亦得之。但专指以下三指三性字。为作三截言性耶。盖在天为理者。即一原之理同也。在物为性者。即异体之理不同也。天命性之性。亦成形上所赋之性。则无论本然偏全。皆从异体后言之也。今于气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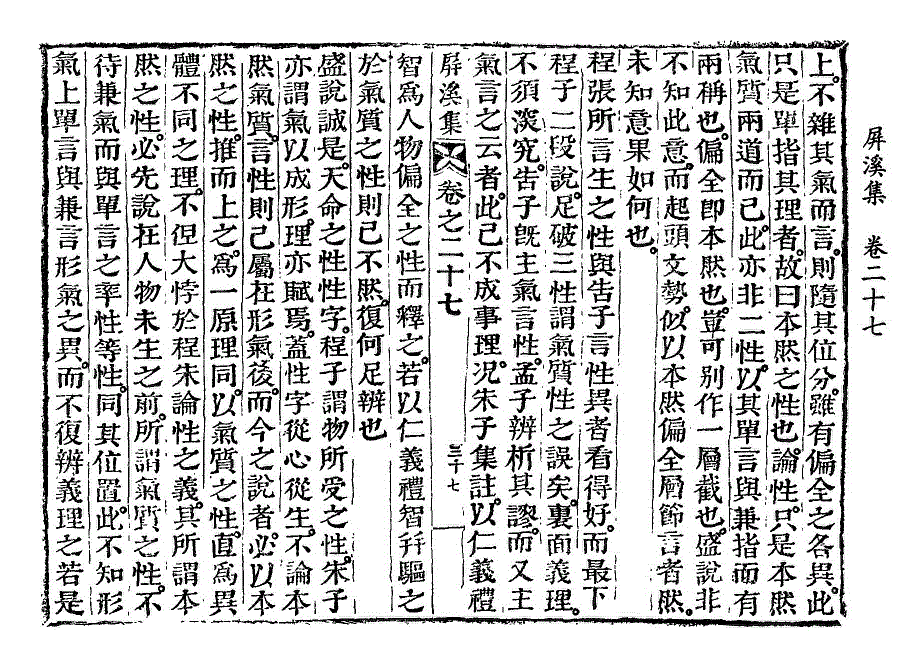 上。不杂其气而言。则随其位分。虽有偏全之各异。此只是单指其理者。故曰本然之性也。论性。只是本然气质两道而已。此亦非二性。以其单言与兼指而有两称也。偏全即本然也。岂可别作一层截也。盛说非不知此意。而起头文势。似以本然偏全层节言者然。未知意果如何也。
上。不杂其气而言。则随其位分。虽有偏全之各异。此只是单指其理者。故曰本然之性也。论性。只是本然气质两道而已。此亦非二性。以其单言与兼指而有两称也。偏全即本然也。岂可别作一层截也。盛说非不知此意。而起头文势。似以本然偏全层节言者然。未知意果如何也。程张所言生之性与告子言性异者看得好。而最下程子二段说。足破三性谓气质性之误矣。里面义理。不须深究。告子既主气言性。孟子辨析其谬。而又主气言之云者。此已不成事理。况朱子集注。以仁义礼智为人物偏全之性而释之。若以仁义礼智并驱之于气质之性则已不然。复何足辨也。
盛说诚是。天命之性性字。程子谓物所受之性。朱子亦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盖性字从心从生。不论本然气质。言性则已属在形气后。而今之说者。必以本然之性。推而上之。为一原理同。以气质之性。直为异体不同之理。不但大悖于程朱论性之义。其所谓本然之性。必先说在人物未生之前。所谓气质之性。不待兼气而与单言之率性等性。同其位置。此不知形气上单言与兼言形气之异。而不复辨义理之若是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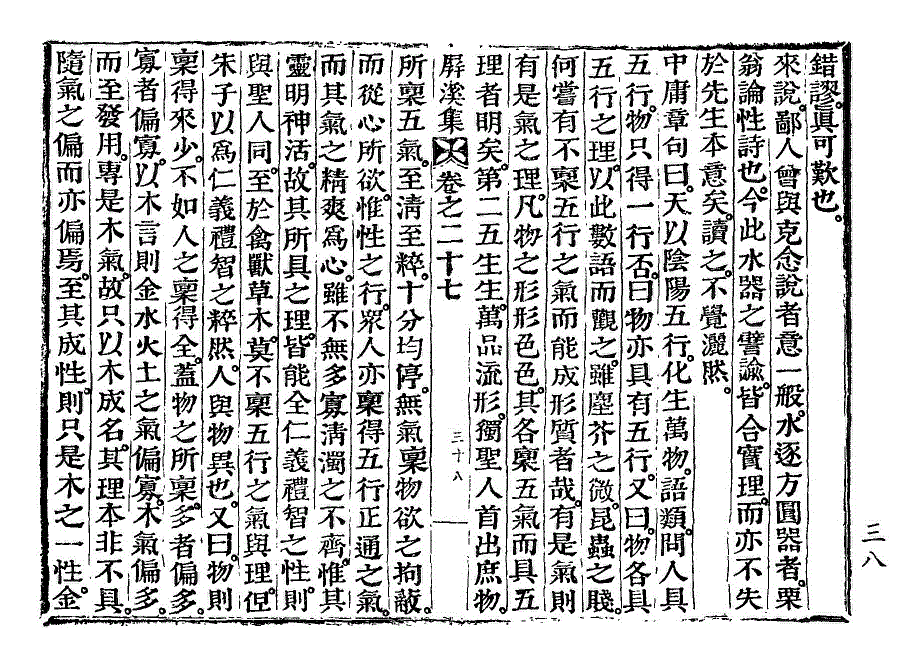 错谬。真可叹也。
错谬。真可叹也。来说。鄙人曾与克念说者意一般。水逐方圆器者。栗翁论性诗也。今此水器之譬谕。皆合实理。而亦不失于先生本意矣。读之。不觉洒然。
中庸章句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语类。问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否。曰物亦具有五行。又曰。物各具五行之理。以此数语而观之。虽尘芥之微。昆虫之贱。何尝有不禀五行之气而能成形质者哉。有是气则有是气之理。凡物之形形色色。其各禀五气而具五理者明矣。第二五生生。万品流形。独圣人首出庶物。所禀五气。至清至粹。十分均停。无气禀物欲之拘蔽。而从心所欲。惟性之行。众人亦禀得五行正通之气。而其气之精爽为心。虽不无多寡清浊之不齐。惟其灵明神活。故其所具之理。皆能全仁义礼智之性。则与圣人同。至于禽兽草木。莫不禀五行之气与理。但朱子以为仁义礼智之粹然。人与物异也。又曰。物则禀得来少。不如人之禀得全。盖物之所禀。多者偏多。寡者偏寡。以木言则金水火土之气偏寡。木气偏多。而至发用。专是木气。故只以木成名。其理本非不具。随气之偏而亦偏焉。至其成性。则只是木之一性。金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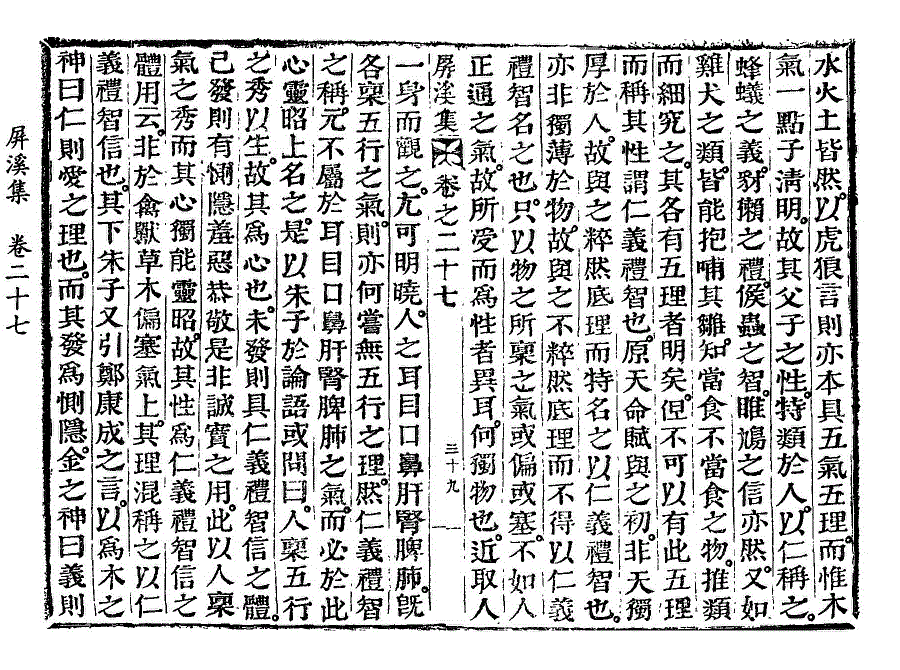 水火土皆然。以虎狼言则亦本具五气五理。而惟木气一点子清明。故其父子之性。特类于人。以仁称之。蜂蚁之义。豺獭之礼。候虫之智。雎鸠之信亦然。又如鸡犬之类。皆能抱哺其雏。知当食不当食之物。推类而细究之。其各有五理者明矣。但不可以有此五理而称其性谓仁义礼智也。原天命赋与之初。非天独厚于人。故与之粹然底理而特名之以仁义礼智也。亦非独薄于物。故与之不粹然底理而不得以仁义礼智名之也。只以物之所禀之气或偏或塞。不如人正通之气。故所受而为性者异耳。何独物也。近取人一身而观之。尤可明晓。人之耳目口鼻肝肾脾肺。既各禀五行之气。则亦何尝无五行之理。然仁义礼智之称。元不属于耳目口鼻肝肾脾肺之气。而必于此心灵昭上名之。是以朱子于论语或问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用。此以人禀气之秀而其心独能灵昭。故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体用云。非于禽兽草木偏塞气上。其理混称之以仁义礼智信也。其下朱子又引郑康成之言。以为木之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金之神曰义则
水火土皆然。以虎狼言则亦本具五气五理。而惟木气一点子清明。故其父子之性。特类于人。以仁称之。蜂蚁之义。豺獭之礼。候虫之智。雎鸠之信亦然。又如鸡犬之类。皆能抱哺其雏。知当食不当食之物。推类而细究之。其各有五理者明矣。但不可以有此五理而称其性谓仁义礼智也。原天命赋与之初。非天独厚于人。故与之粹然底理而特名之以仁义礼智也。亦非独薄于物。故与之不粹然底理而不得以仁义礼智名之也。只以物之所禀之气或偏或塞。不如人正通之气。故所受而为性者异耳。何独物也。近取人一身而观之。尤可明晓。人之耳目口鼻肝肾脾肺。既各禀五行之气。则亦何尝无五行之理。然仁义礼智之称。元不属于耳目口鼻肝肾脾肺之气。而必于此心灵昭上名之。是以朱子于论语或问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用。此以人禀气之秀而其心独能灵昭。故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体用云。非于禽兽草木偏塞气上。其理混称之以仁义礼智信也。其下朱子又引郑康成之言。以为木之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金之神曰义则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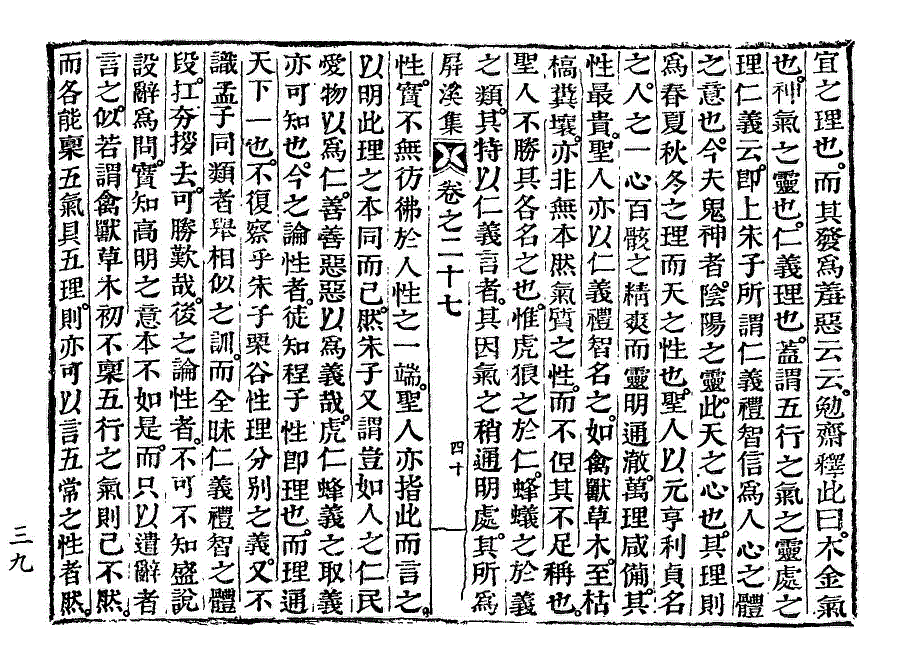 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云云。勉斋释此曰。木金气也。神气之灵也。仁义理也。盖谓五行之气之灵处之理仁义云。即上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信为人心之体之意也。今夫鬼神者。阴阳之灵。此天之心也。其理则为春夏秋冬之理而天之性也。圣人以元亨利贞名之。人之一心百骸之精爽而灵明通澈。万理咸备。其性最贵。圣人亦以仁义礼智名之。如禽兽草木。至枯槁粪壤。亦非无本然气质之性。而不但其不足称也。圣人不胜其各名之也。惟虎狼之于仁。蜂蚁之于义之类。其特以仁义言者。其因气之稍通明处。其所为性。实不无彷佛于人性之一端。圣人亦指此而言之。以明此理之本同而已。然朱子又谓岂如人之仁民爱物以为仁。善善恶恶以为义哉。虎仁蜂义之取义亦可知也。今之论性者。徒知程子性即理也。而理通天下一也。不复察乎朱子栗谷性理分别之义。又不识孟子同类者举相似之训。而全昧仁义礼智之体段。扛夯拶去。可胜叹哉。后之论性者。不可不知盛说设辞为问。实知高明之意本不如是。而只以遣辞者言之。似若谓禽兽草木初不禀五行之气则已不然。而各能禀五气具五理。则亦可以言五常之性者然。
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云云。勉斋释此曰。木金气也。神气之灵也。仁义理也。盖谓五行之气之灵处之理仁义云。即上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信为人心之体之意也。今夫鬼神者。阴阳之灵。此天之心也。其理则为春夏秋冬之理而天之性也。圣人以元亨利贞名之。人之一心百骸之精爽而灵明通澈。万理咸备。其性最贵。圣人亦以仁义礼智名之。如禽兽草木。至枯槁粪壤。亦非无本然气质之性。而不但其不足称也。圣人不胜其各名之也。惟虎狼之于仁。蜂蚁之于义之类。其特以仁义言者。其因气之稍通明处。其所为性。实不无彷佛于人性之一端。圣人亦指此而言之。以明此理之本同而已。然朱子又谓岂如人之仁民爱物以为仁。善善恶恶以为义哉。虎仁蜂义之取义亦可知也。今之论性者。徒知程子性即理也。而理通天下一也。不复察乎朱子栗谷性理分别之义。又不识孟子同类者举相似之训。而全昧仁义礼智之体段。扛夯拶去。可胜叹哉。后之论性者。不可不知盛说设辞为问。实知高明之意本不如是。而只以遣辞者言之。似若谓禽兽草木初不禀五行之气则已不然。而各能禀五气具五理。则亦可以言五常之性者然。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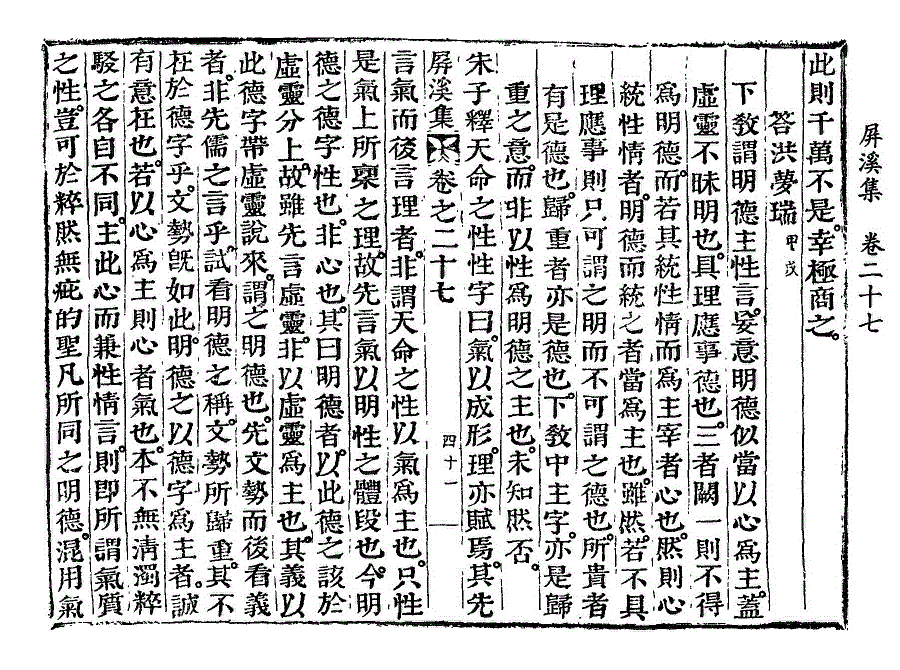 此则千万不是。幸极商之。
此则千万不是。幸极商之。答洪梦瑞(甲戌)
下教谓明德主性言。妄意明德似当以心为主。盖虚灵不昧明也。具理应事德也。三者阙一则不得为明德。而若其统性情而为主宰者心也。然则心统性情者。明德而统之者当为主也。虽然。若不具理应事则只可谓之明而不可谓之德也。所贵者有是德也。归重者亦是德也。下教中主字。亦是归重之意。而非以性为明德之主也。未知然否。
朱子释天命之性性字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其先言气而后言理者。非谓天命之性以气为主也。只性是气上所禀之理。故先言气以明性之体段也。今明德之德字性也。非心也。其曰明德者。以此德之该于虚灵分上。故虽先言虚灵。非以虚灵为主也。其义以此德字带虚灵说来。谓之明德也。先文势而后看义者。非先儒之言乎。试看明德之称。文势所归重。其不在于德字乎。文势既如此。明德之以德字为主者。诚有意在也。若以心为主则心者气也。本不无清浊粹驳之各自不同。主此心而兼性情言。则即所谓气质之性。岂可于粹然无疵的圣凡所同之明德。混用气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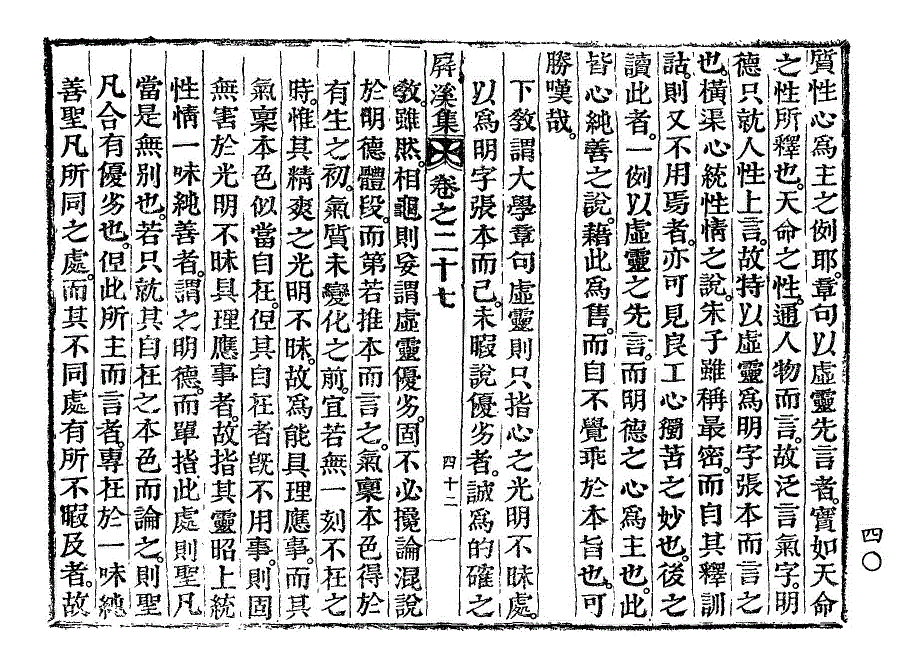 质性心为主之例耶。章句以虚灵先言者。实如天命之性所释也。天命之性。通人物而言。故泛言气字。明德只就人性上言。故特以虚灵为明字张本而言之也。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朱子虽称最密。而自其释训诂。则又不用焉者。亦可见良工心独苦之妙也。后之读此者。一例以虚灵之先言。而明德之心为主也。此皆心纯善之说。藉此为售。而自不觉乖于本旨也。可胜叹哉。
质性心为主之例耶。章句以虚灵先言者。实如天命之性所释也。天命之性。通人物而言。故泛言气字。明德只就人性上言。故特以虚灵为明字张本而言之也。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朱子虽称最密。而自其释训诂。则又不用焉者。亦可见良工心独苦之妙也。后之读此者。一例以虚灵之先言。而明德之心为主也。此皆心纯善之说。藉此为售。而自不觉乖于本旨也。可胜叹哉。下教谓大学章句虚灵则只指心之光明不昧处。以为明字张本而已。未暇说优劣者。诚为的确之教。虽然。相龟则妄谓虚灵优劣。固不必搀论混说于明德体段。而第若推本而言之。气禀本色得于有生之初。气质未变化之前。宜若无一刻不在之时。惟其精爽之光明不昧。故为能具理应事。而其气禀本色似当自在。但其自在者既不用事。则固无害于光明不昧具理应事者。故指其灵昭上统性情一味纯善者。谓之明德。而单指此处则圣凡当是无别也。若只就其自在之本色而论之。则圣凡合有优劣也。但此所主而言者。专在于一味纯善圣凡所同之处。而其不同处有所不暇及者。故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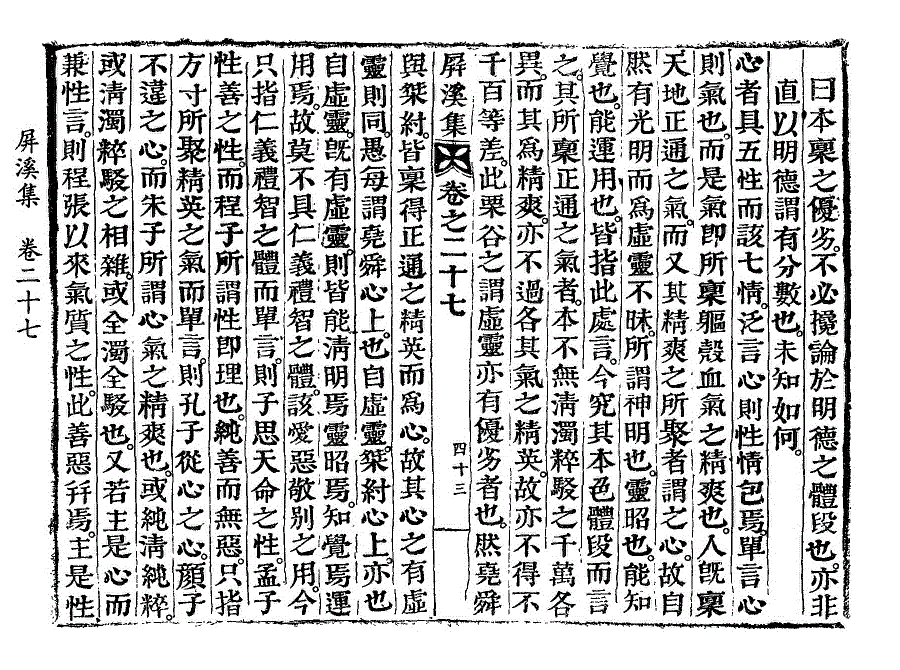 曰本禀之优劣。不必搀论于明德之体段也。亦非直以明德谓有分数也。未知如何。
曰本禀之优劣。不必搀论于明德之体段也。亦非直以明德谓有分数也。未知如何。心者具五性而该七情。泛言心则性情包焉。单言心则气也。而是气即所禀躯壳血气之精爽也。人既禀天地正通之气。而又其精爽之所聚者谓之心。故自然有光明而为虚灵不昧。所谓神明也。灵昭也。能知觉也。能运用也。皆指此处言。今究其本色体段而言之。其所禀正通之气者。本不无清浊粹驳之千万各异。而其为精爽。亦不过各其气之精英。故亦不得不千百等差。此栗谷之谓虚灵亦有优劣者也。然尧舜与桀纣。皆禀得正通之精英而为心。故其心之有虚灵则同。愚每谓尧舜心上。也自虚灵。桀纣心上。亦也自虚灵。既有虚灵。则皆能清明焉灵昭焉。知觉焉运用焉。故莫不具仁义礼智之体。该爱恶敬别之用。今只指仁义礼智之体而单言。则子思天命之性。孟子性善之性。而程子所谓性即理也。纯善而无恶。只指方寸所聚精英之气而单言。则孔子从心之心。颜子不违之心。而朱子所谓心气之精爽也。或纯清纯粹。或清浊粹驳之相杂。或全浊全驳也。又若主是心而兼性言。则程张以来气质之性。此善恶并焉。主是性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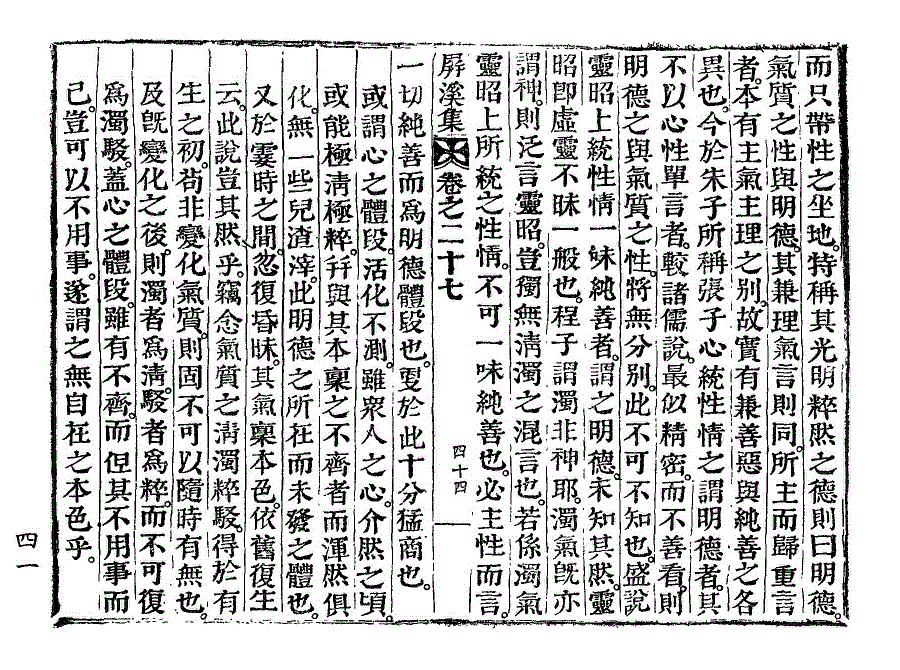 而只带性之坐地。特称其光明粹然之德则曰明德。气质之性与明德。其兼理气言则同。所主而归重言者。本有主气主理之别。故实有兼善恶与纯善之各异也。今于朱子所称张子心统性情之谓明德者。其不以心性单言者。较诸儒说。最似精密。而不善看。则明德之与气质之性。将无分别。此不可不知也。盛说灵昭上统性情一味纯善者。谓之明德。未知其然。灵昭即虚灵不昧一般也。程子谓浊非神耶。浊气既亦谓神。则泛言灵昭。岂独无清浊之混言也。若系浊气灵昭上所统之性情。不可一味纯善也。必主性而言。一切纯善而为明德体段也。更于此十分猛商也。
而只带性之坐地。特称其光明粹然之德则曰明德。气质之性与明德。其兼理气言则同。所主而归重言者。本有主气主理之别。故实有兼善恶与纯善之各异也。今于朱子所称张子心统性情之谓明德者。其不以心性单言者。较诸儒说。最似精密。而不善看。则明德之与气质之性。将无分别。此不可不知也。盛说灵昭上统性情一味纯善者。谓之明德。未知其然。灵昭即虚灵不昧一般也。程子谓浊非神耶。浊气既亦谓神。则泛言灵昭。岂独无清浊之混言也。若系浊气灵昭上所统之性情。不可一味纯善也。必主性而言。一切纯善而为明德体段也。更于此十分猛商也。或谓心之体段。活化不测。虽众人之心。介然之顷。或能极清极粹。并与其本禀之不齐者而浑然俱化。无一些儿渣滓。此明德之所在而未发之体也。又于霎时之间。忽复昏昧。其气禀本色。依旧复生云。此说岂其然乎。窃念气质之清浊粹驳。得于有生之初。苟非变化气质。则固不可以随时有无也。及既变化之后。则浊者为清。驳者为粹。而不可复为浊驳。盖心之体段。虽有不齐。而但其不用事而已。岂可以不用事。遂谓之无自在之本色乎。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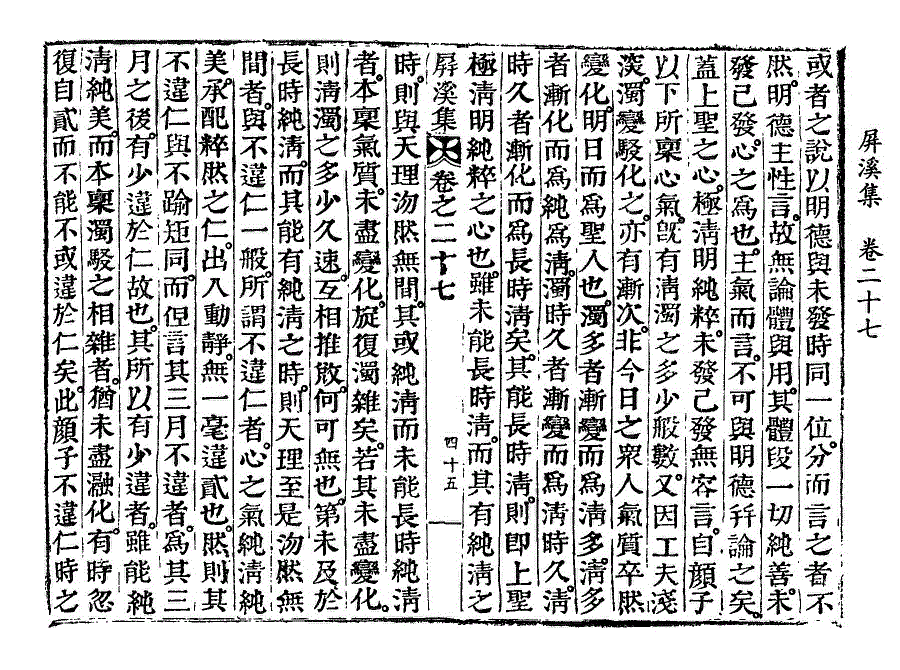 或者之说以明德与未发时同一位。分而言之者不然。明德主性言。故无论体与用。其体段一切纯善。未发已发。心之为也。主气而言。不可与明德并论之矣。盖上圣之心。极清明纯粹。未发已发无容言。自颜子以下所禀心气。既有清浊之多少般数。又因工夫浅深。浊变驳化之。亦有渐次。非今日之众人气质卒然变化。明日而为圣人也。浊多者渐变而为清多。清多者渐化而为纯为清。浊时久者渐变而为清时久。清时久者渐化而为长时清矣。其能长时清。则即上圣极清明纯粹之心也。虽未能长时清。而其有纯清之时。则与天理沕然无间。其或纯清而未能长时纯清者。本禀气质。未尽变化。旋复浊杂矣。若其未尽变化。则清浊之多少久速。互相推敚。何可无也。第未及于长时纯清。而其能有纯清之时。则天理至是沕然无间者。与不违仁一般。所谓不违仁者。心之气纯清纯美。承配粹然之仁。出入动静。无一毫违贰也。然则其不违仁与不踰矩同。而但言其三月不违者。为其三月之后。有少违于仁故也。其所以有少违者。虽能纯清纯美。而本禀浊驳之相杂者。犹未尽瀜化。有时忽复自贰而不能不或违于仁矣。此颜子不违仁时之
或者之说以明德与未发时同一位。分而言之者不然。明德主性言。故无论体与用。其体段一切纯善。未发已发。心之为也。主气而言。不可与明德并论之矣。盖上圣之心。极清明纯粹。未发已发无容言。自颜子以下所禀心气。既有清浊之多少般数。又因工夫浅深。浊变驳化之。亦有渐次。非今日之众人气质卒然变化。明日而为圣人也。浊多者渐变而为清多。清多者渐化而为纯为清。浊时久者渐变而为清时久。清时久者渐化而为长时清矣。其能长时清。则即上圣极清明纯粹之心也。虽未能长时清。而其有纯清之时。则与天理沕然无间。其或纯清而未能长时纯清者。本禀气质。未尽变化。旋复浊杂矣。若其未尽变化。则清浊之多少久速。互相推敚。何可无也。第未及于长时纯清。而其能有纯清之时。则天理至是沕然无间者。与不违仁一般。所谓不违仁者。心之气纯清纯美。承配粹然之仁。出入动静。无一毫违贰也。然则其不违仁与不踰矩同。而但言其三月不违者。为其三月之后。有少违于仁故也。其所以有少违者。虽能纯清纯美。而本禀浊驳之相杂者。犹未尽瀜化。有时忽复自贰而不能不或违于仁矣。此颜子不违仁时之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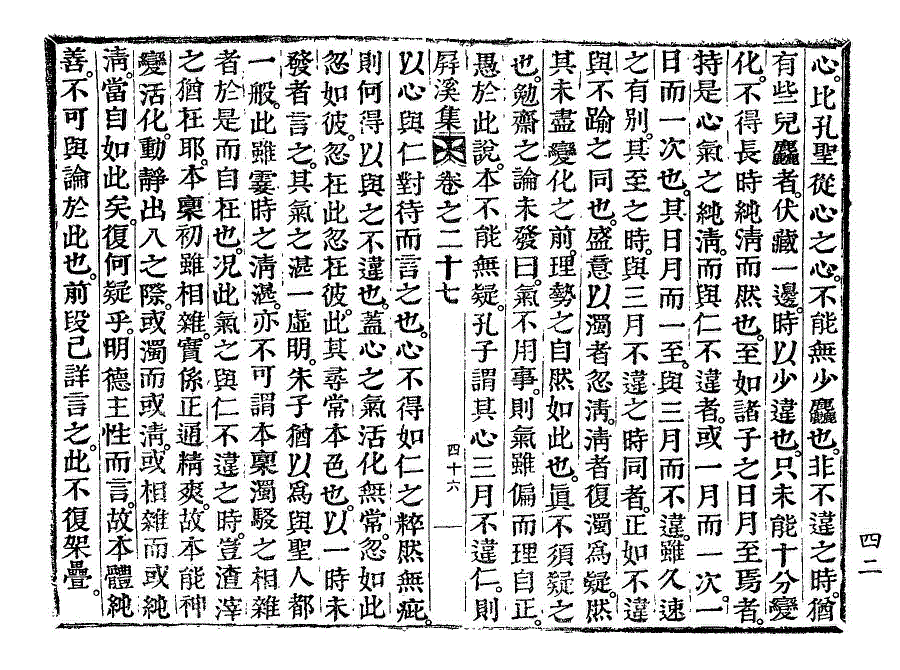 心。比孔圣从心之心。不能无少粗也。非不违之时。犹有些儿粗者。伏藏一边。时以少违也。只未能十分变化。不得长时纯清而然也。至如诸子之日月至焉者。特是心气之纯清。而与仁不违者。或一月而一次。一日而一次也。其日月而一至。与三月而不违。虽久速之有别。其至之时。与三月不违之时同者。正如不违与不踰之同也。盛意以浊者忽清。清者复浊为疑。然其未尽变化之前。理势之自然如此也。真不须疑之也。勉斋之论未发曰。气不用事。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愚于此说。本不能无疑。孔子谓其心三月不违仁。则以心与仁对待而言之也。心不得如仁之粹然无疵。则何得以与之不违也。盖心之气活化无常。忽如此忽如彼。忽在此忽在彼。此其寻常本色也。以一时未发者言之。其气之湛一虚明。朱子犹以为与圣人都一般。此虽霎时之清湛。亦不可谓本禀浊驳之相杂者于是而自在也。况此气之与仁不违之时。岂渣滓之犹在耶。本禀初虽相杂。实系正通精爽。故本能神变活化。动静出入之际。或浊而或清。或相杂而或纯清。当自如此矣。复何疑乎。明德主性而言。故本体纯善。不可与论于此也。前段已详言之。此不复架叠。
心。比孔圣从心之心。不能无少粗也。非不违之时。犹有些儿粗者。伏藏一边。时以少违也。只未能十分变化。不得长时纯清而然也。至如诸子之日月至焉者。特是心气之纯清。而与仁不违者。或一月而一次。一日而一次也。其日月而一至。与三月而不违。虽久速之有别。其至之时。与三月不违之时同者。正如不违与不踰之同也。盛意以浊者忽清。清者复浊为疑。然其未尽变化之前。理势之自然如此也。真不须疑之也。勉斋之论未发曰。气不用事。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愚于此说。本不能无疑。孔子谓其心三月不违仁。则以心与仁对待而言之也。心不得如仁之粹然无疵。则何得以与之不违也。盖心之气活化无常。忽如此忽如彼。忽在此忽在彼。此其寻常本色也。以一时未发者言之。其气之湛一虚明。朱子犹以为与圣人都一般。此虽霎时之清湛。亦不可谓本禀浊驳之相杂者于是而自在也。况此气之与仁不违之时。岂渣滓之犹在耶。本禀初虽相杂。实系正通精爽。故本能神变活化。动静出入之际。或浊而或清。或相杂而或纯清。当自如此矣。复何疑乎。明德主性而言。故本体纯善。不可与论于此也。前段已详言之。此不复架叠。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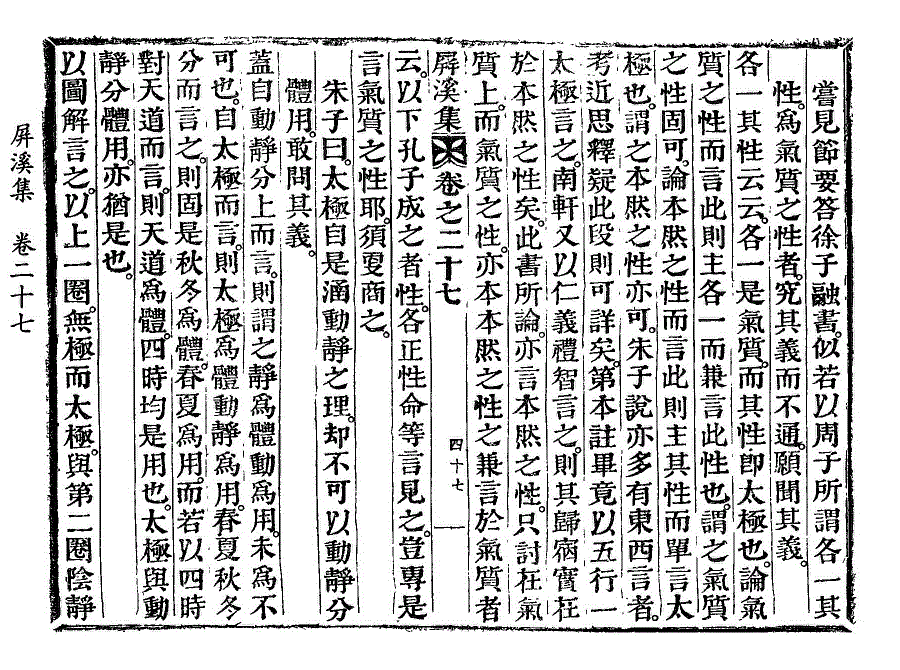 尝见节要答徐子融书。似若以周子所谓各一其性。为气质之性者。究其义而不通。愿闻其义。
尝见节要答徐子融书。似若以周子所谓各一其性。为气质之性者。究其义而不通。愿闻其义。各一其性云云。各一是气质。而其性即太极也。论气质之性而言此则主各一而兼言此性也。谓之气质之性固可。论本然之性而言此则主其性而单言太极也。谓之本然之性亦可。朱子说亦多有东西言者。考近思释疑此段则可详矣。第本注毕竟以五行一太极言之。南轩又以仁义礼智言之。则其归宿实在于本然之性矣。此书所论。亦言本然之性。只讨在气质上。而气质之性。亦本本然之性之兼言于气质者云。以下孔子成之者性。各正性命等言见之。岂专是言气质之性耶。须更商之。
朱子曰。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敢问其义。
盖自动静分上而言。则谓之静为体动为用。未为不可也。自太极而言。则太极为体动静为用。春夏秋冬分而言之。则固是秋冬为体。春夏为用。而若以四时对天道而言。则天道为体。四时均是用也。太极与动静分体用。亦犹是也。
以图解言之。以上一圈。无极而太极。与第二圈阴静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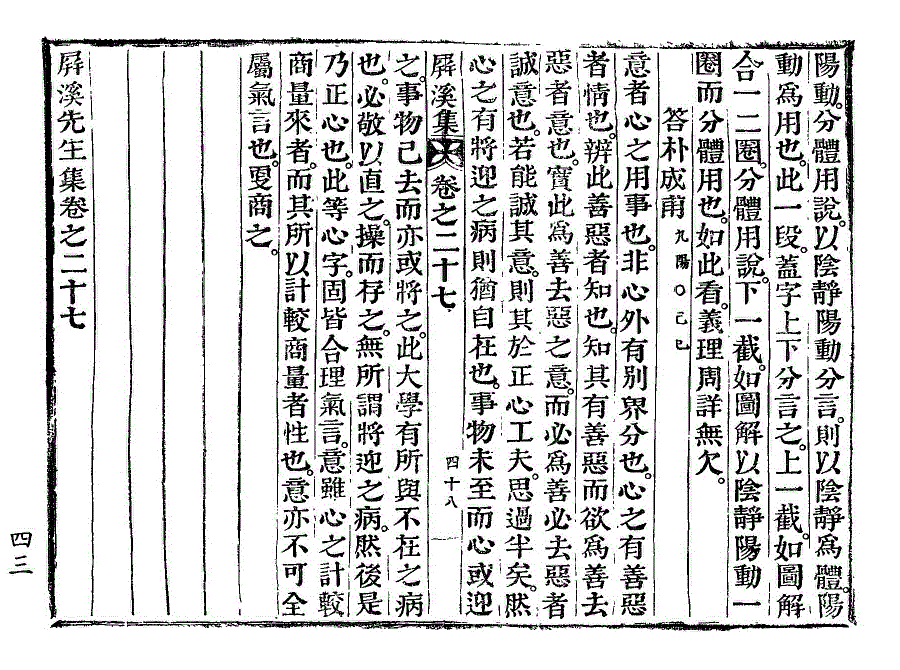 阳动。分体用说。以阴静阳动分言。则以阴静为体。阳动为用也。此一段。盖字上下分言之。上一截。如图解合一二圈。分体用说。下一截。如图解以阴静阳动一圈而分体用也。如此看。义理周详无欠。
阳动。分体用说。以阴静阳动分言。则以阴静为体。阳动为用也。此一段。盖字上下分言之。上一截。如图解合一二圈。分体用说。下一截。如图解以阴静阳动一圈而分体用也。如此看。义理周详无欠。答朴成甫(九阳○己巳)
意者心之用事也。非心外有别界分也。心之有善恶者情也。辨此善恶者知也。知其有善恶而欲为善去恶者意也。实此为善去恶之意。而必为善必去恶者诚意也。若能诚其意。则其于正心工夫。思过半矣。然心之有将迎之病则犹自在也。事物未至而心或迎之。事物已去而亦或将之。此大学有所与不在之病也。必敬以直之。操而存之。无所谓将迎之病。然后是乃正心也。此等心字。固皆合理气言。意虽心之计较商量来者。而其所以计较商量者性也。意亦不可全属气言也。更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