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书
书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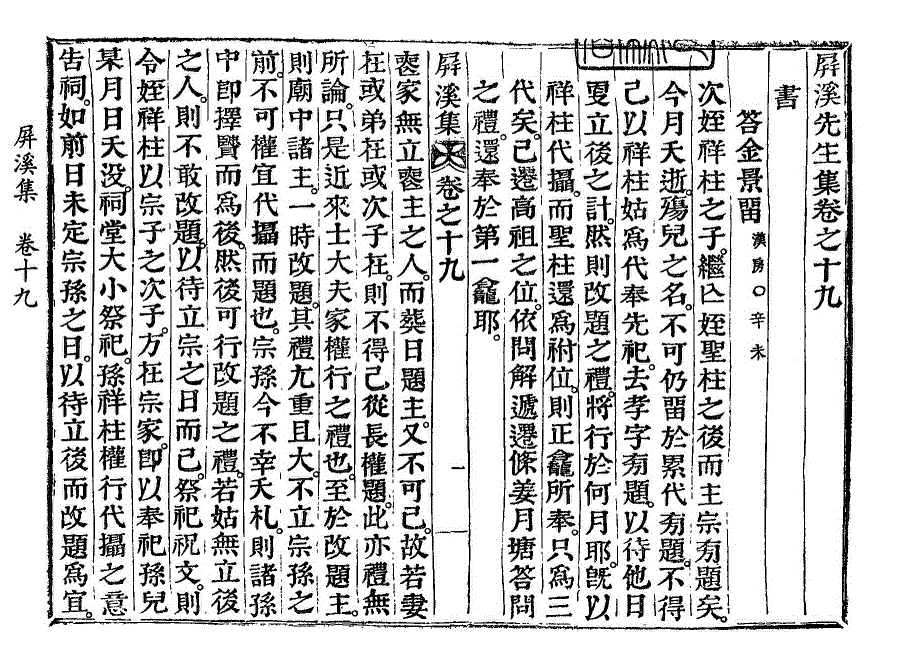 答金景留(汉房○辛未)
答金景留(汉房○辛未)次侄祥柱之子。继亡侄圣柱之后而主宗旁题矣。今月夭逝。殇儿之名。不可仍留于累代旁题。不得已以祥柱姑为代奉先祀。去孝字旁题。以待他日更立后之计。然则改题之礼。将行于何月耶。既以祥柱代摄。而圣柱还为祔位。则正龛所奉。只为三代矣。已迁高祖之位。依问解递迁条姜月塘答问之礼。还奉于第一龛耶。
丧家无立丧主之人。而葬日题主。又不可已。故若妻在或弟在或次子在。则不得已从长权题。此亦礼无所论。只是近来士大夫家权行之礼也。至于改题主。则庙中诸主。一时改题。其礼尤重且大。不立宗孙之前。不可权宜代摄而题也。宗孙今不幸夭札。则诸孙中即择贤而为后。然后可行改题之礼。若姑无立后之人。则不敢改题。以待立宗之日而已。祭祀祝文。则令侄祥柱以宗子之次子。方在宗家。即以奉祀孙儿某月日夭没。祠堂大小祭祀。孙祥柱权行代摄之意告祠。如前日未定宗孙之日。以待立后而改题为宜。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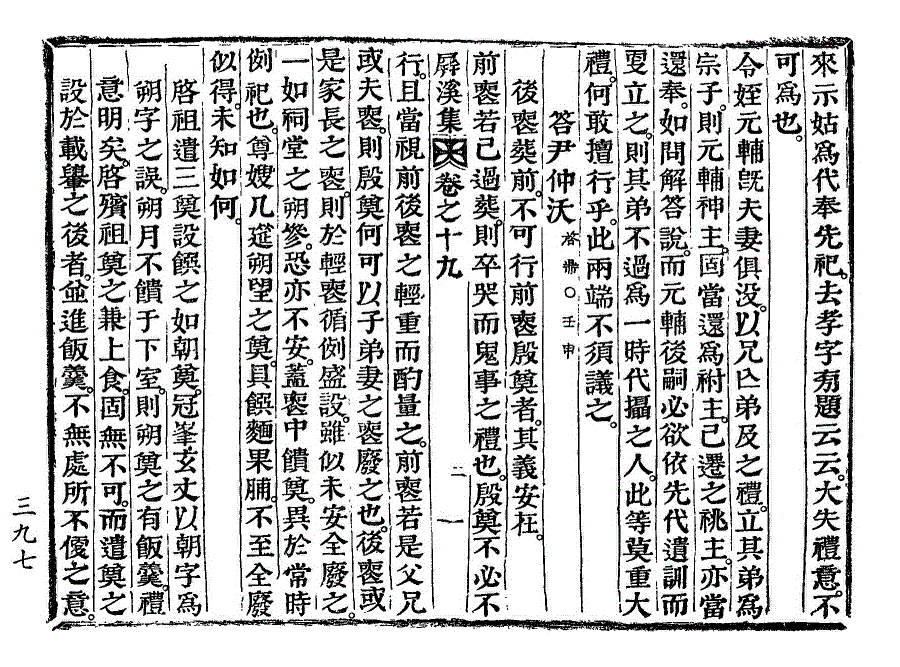 来示姑为代奉先祀。去孝字旁题云云。大失礼意。不可为也。
来示姑为代奉先祀。去孝字旁题云云。大失礼意。不可为也。令侄元辅既夫妻俱没。以兄亡弟及之礼。立其弟为宗子。则元辅神主。固当还为祔主。已迁之祧主。亦当还奉。如问解答说。而元辅后嗣必欲依先代遗训而更立之。则其弟不过为一时代摄之人。此等莫重大礼。何敢擅行乎。此两端不须议之。
答尹仲沃(启鼎○壬申)
后丧葬前。不可行前丧殷奠者。其义安在。
前丧若已过葬。则卒哭而鬼事之礼也。殷奠不必不行。且当视前后丧之轻重而酌量之。前丧若是父兄或夫丧。则殷奠何可以子弟妻之丧废之也。后丧或是家长之丧。则于轻丧循例盛设。虽似未安全废之。一如祠堂之朔参。恐亦不安。盖丧中馈奠。异于常时例祀也。尊嫂几筵朔望之奠。具馔面果脯。不至全废似得。未知如何。
启祖遣三奠设馔之如朝奠。冠峰,玄丈以朝字为朔字之误。朔月不馈于下室。则朔奠之有饭羹。礼意明矣。启殡祖奠之兼上食。固无不可。而遣奠之设于载舆之后者。并进饭羹。不无处所不便之意。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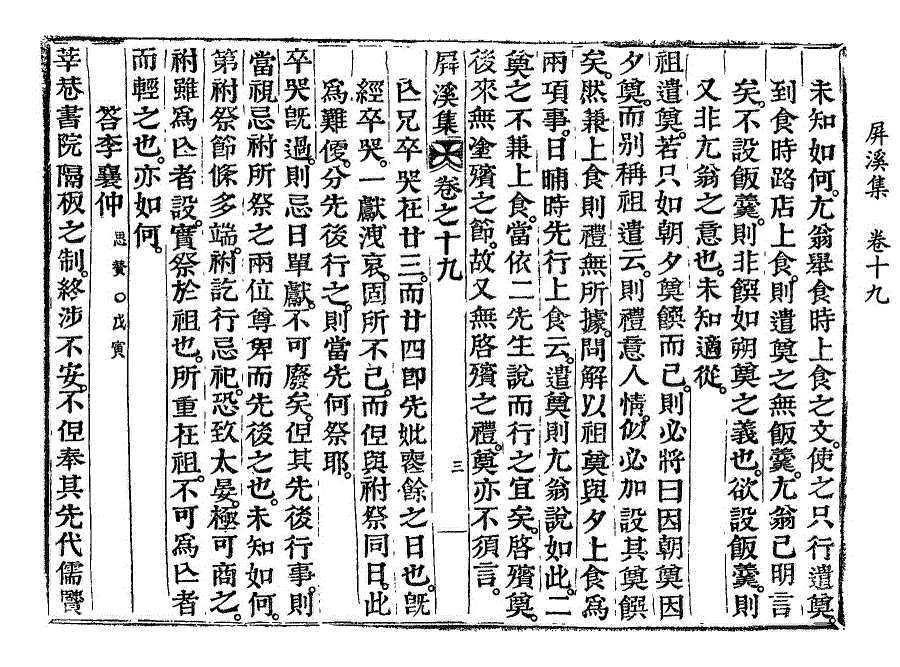 未知如何。尤翁举食时上食之文。使之只行遣奠。到食时路店上食。则遣奠之无饭羹。尤翁已明言矣。不设饭羹。则非馔如朔奠之义也。欲设饭羹。则又非尤翁之意也。未知适从。
未知如何。尤翁举食时上食之文。使之只行遣奠。到食时路店上食。则遣奠之无饭羹。尤翁已明言矣。不设饭羹。则非馔如朔奠之义也。欲设饭羹。则又非尤翁之意也。未知适从。祖遣奠。若只如朝夕奠馔而已。则必将曰因朝奠因夕奠。而别称祖遣云。则礼意人情。似必加设其奠馔矣。然兼上食则礼无所据。问解以祖奠与夕上食为两项事。日晡时先行上食云。遣奠则尤翁说如此。二奠之不兼上食。当依二先生说而行之宜矣。启殡奠。后来无涂殡之节。故又无启殡之礼。奠亦不须言。
亡兄卒哭在廿三。而廿四即先妣丧馀之日也。既经卒哭。一献泄哀。固所不已。而但与祔祭同日。此为难便。分先后行之。则当先何祭耶。
卒哭既过。则忌日单献。不可废矣。但其先后行事。则当视忌祔所祭之两位尊卑而先后之也。未知如何。第祔祭节条多端。祔讫行忌祀。恐致太晏。极可商之。祔虽为亡者设。实祭于祖也。所重在祖。不可为亡者而轻之也。亦如何。
答李襄仲(思赞○戊寅)
莘巷书院隔板之制。终涉不安。不但奉其先代儒贤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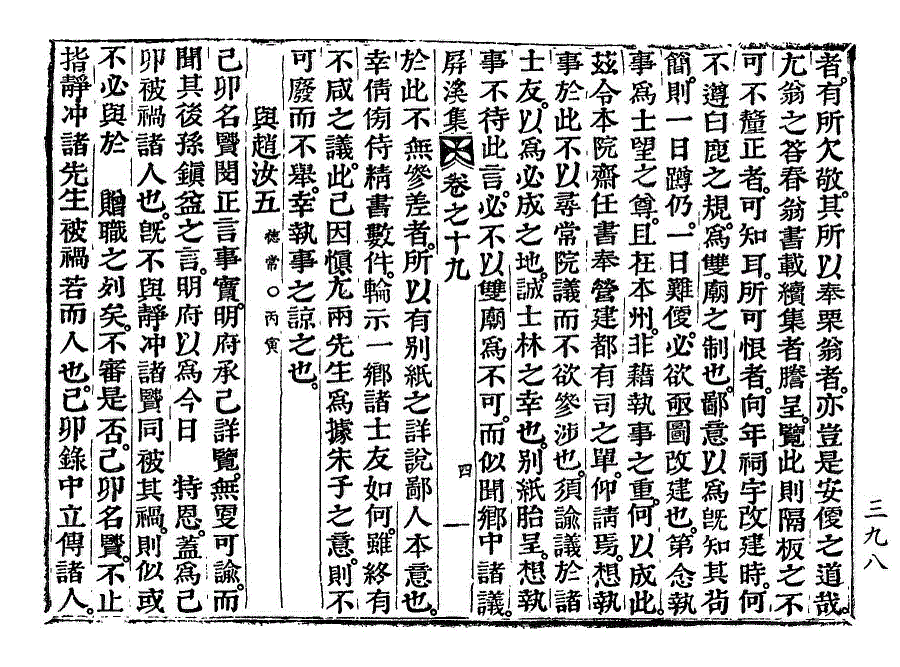 者。有所欠敬。其所以奉栗翁者。亦岂是安便之道哉。尤翁之答春翁书载续集者誊呈。览此则隔板之不可不釐正者。可知耳。所可恨者。向年祠宇改建时。何不遵白鹿之规。为双庙之制也。鄙意以为既知其苟简。则一日蹲仍。一日难便。必欲亟图改建也。第念执事为士望之尊。且在本州。非藉执事之重。何以成此。玆令本院斋任书奉营建都有司之单。仰请焉。想执事于此不以寻常院议而不欲参涉也。须谕议于诸士友。以为必成之地。诚士林之幸也。别纸胎呈。想执事不待此言。必不以双庙为不可。而似闻乡中诸议。于此不无参差者。所以有别纸之详说鄙人本意也。幸倩傍侍精书数件。轮示一乡诸士友如何。虽终有不咸之议。此已因慎,尤两先生为据朱子之意。则不可废而不举。幸执事之谅之也。
者。有所欠敬。其所以奉栗翁者。亦岂是安便之道哉。尤翁之答春翁书载续集者誊呈。览此则隔板之不可不釐正者。可知耳。所可恨者。向年祠宇改建时。何不遵白鹿之规。为双庙之制也。鄙意以为既知其苟简。则一日蹲仍。一日难便。必欲亟图改建也。第念执事为士望之尊。且在本州。非藉执事之重。何以成此。玆令本院斋任书奉营建都有司之单。仰请焉。想执事于此不以寻常院议而不欲参涉也。须谕议于诸士友。以为必成之地。诚士林之幸也。别纸胎呈。想执事不待此言。必不以双庙为不可。而似闻乡中诸议。于此不无参差者。所以有别纸之详说鄙人本意也。幸倩傍侍精书数件。轮示一乡诸士友如何。虽终有不咸之议。此已因慎,尤两先生为据朱子之意。则不可废而不举。幸执事之谅之也。与赵汝五(德常○丙寅)
己卯名贤闵正言事实。明府承已详览。无更可谕。而闻其后孙镇益之言。明府以为今日 特恩。盖为己卯被祸诸人也。既不与静,冲诸贤同被其祸。则似或不必与于 赠职之列矣。不审是否。己卯名贤。不止指静,冲诸先生被祸若而人也。己卯录中立传诸人。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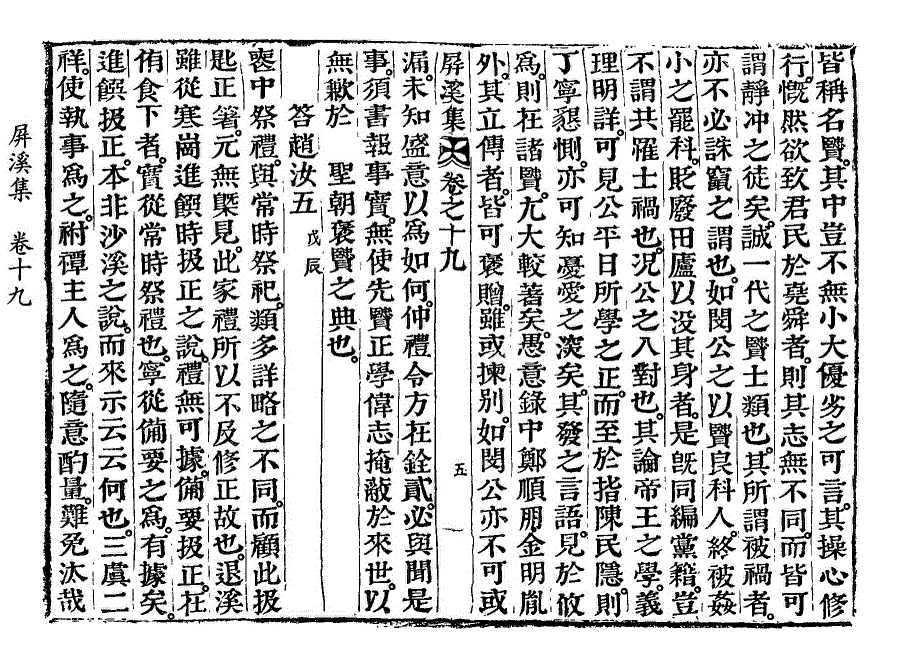 皆称名贤。其中岂不无小大优劣之可言。其操心修行。慨然欲致君民于尧舜者。则其志无不同。而皆可谓静冲之徒矣。诚一代之贤士类也。其所谓被祸者。亦不必诛窜之谓也。如闵公之以贤良科人。终被奸小之罢科。贬废田庐以没其身者。是既同编党籍。岂不谓共罹士祸也。况公之入对也。其论帝王之学。义理明详。可见公平日所学之正。而至于指陈民隐。则丁宁恳恻。亦可知忧爱之深矣。其发之言语。见于攸为。则在诸贤。尤大较著矣。愚意录中郑顺朋,金明胤外。其立传者。皆可褒赠。虽或拣别。如闵公亦不可或漏。未知盛意以为如何。仲礼令方在铨贰。必与闻是事。须书报事实。无使先贤正学伟志掩蔽于来世。以无歉于 圣朝褒贤之典也。
皆称名贤。其中岂不无小大优劣之可言。其操心修行。慨然欲致君民于尧舜者。则其志无不同。而皆可谓静冲之徒矣。诚一代之贤士类也。其所谓被祸者。亦不必诛窜之谓也。如闵公之以贤良科人。终被奸小之罢科。贬废田庐以没其身者。是既同编党籍。岂不谓共罹士祸也。况公之入对也。其论帝王之学。义理明详。可见公平日所学之正。而至于指陈民隐。则丁宁恳恻。亦可知忧爱之深矣。其发之言语。见于攸为。则在诸贤。尤大较著矣。愚意录中郑顺朋,金明胤外。其立传者。皆可褒赠。虽或拣别。如闵公亦不可或漏。未知盛意以为如何。仲礼令方在铨贰。必与闻是事。须书报事实。无使先贤正学伟志掩蔽于来世。以无歉于 圣朝褒贤之典也。答赵汝五(戊辰)
丧中祭礼。与常时祭祀。类多详略之不同。而顾此扱匙正箸。元无槩见。此家礼所以不及修正故也。退溪虽从寒岗进馔时扱正之说。礼无可据。备要扱正。在侑食下者。实从常时祭礼也。宁从备要之为。有据矣。进馔扱正。本非沙溪之说。而来示云云何也。三虞二祥。使执事为之。祔禫主人为之。随意酌量。难免汰哉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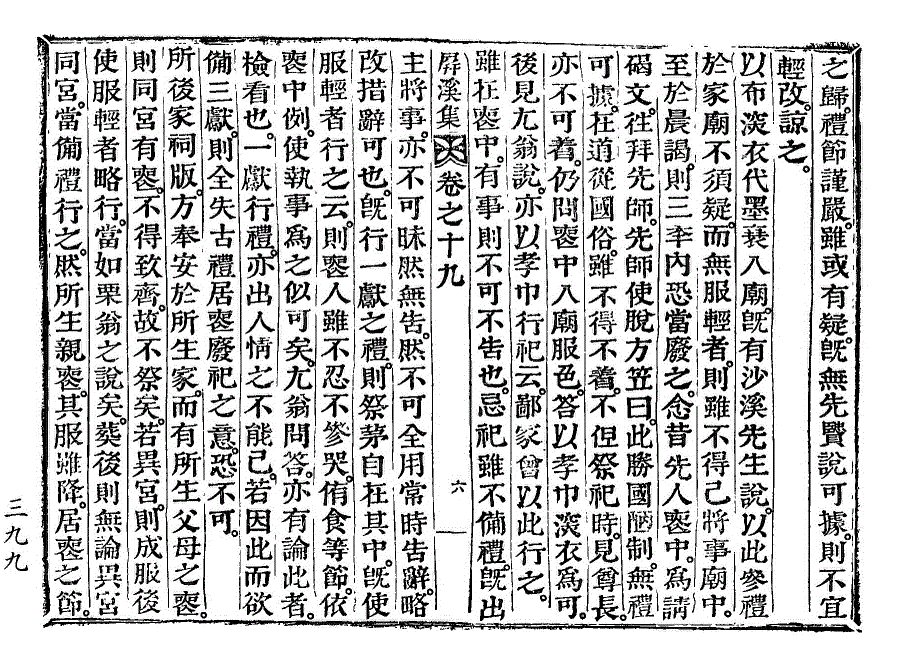 之归。礼节谨严。虽或有疑。既无先贤说可据。则不宜轻改。谅之。
之归。礼节谨严。虽或有疑。既无先贤说可据。则不宜轻改。谅之。以布深衣代墨衰入庙。既有沙溪先生说。以此参礼于家庙不须疑。而无服轻者。则虽不得已将事庙中。至于晨谒。则三年内恐当废之。念昔先人丧中。为请碣文。往拜先师。先师使脱方笠曰。此胜国陋制。无礼可据。在道从国俗。虽不得不着。不但祭祀时。见尊长。亦不可着。仍问丧中入庙服色。答以孝巾深衣为可。后见尤翁说。亦以孝巾行祀云。鄙家曾以此行之。
虽在丧中。有事则不可不告也。忌祀虽不备礼。既出主将事。亦不可昧然无告。然不可全用常时告辞。略改措辞可也。既行一献之礼。则祭茅自在其中。既使服轻者行之云。则丧人虽不忍不参哭。侑食等节。依丧中例。使执事为之似可矣。尤翁问答。亦有论此者。检看也。一献行礼。亦出人情之不能已。若因此而欲备三献。则全失古礼居丧废祀之意。恐不可。
所后家祠版。方奉安于所生家。而有所生父母之丧。则同宫有丧。不得致齐。故不祭矣。若异宫。则成服后使服轻者略行。当如栗翁之说矣。葬后则无论异宫同宫。当备礼行之。然所生亲丧。其服虽降。居丧之节。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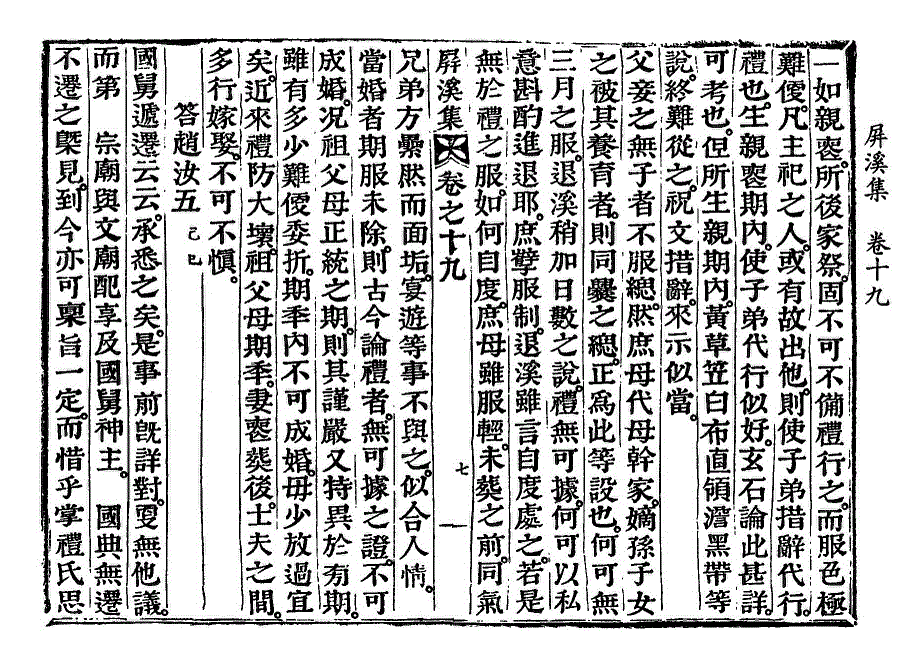 一如亲丧。所后家祭。固不可不备礼行之。而服色极难便。凡主祀之人。或有故出他。则使子弟措辞代行。礼也。生亲丧期内。使子弟代行似好。玄石论此甚详。可考也。但所生亲期内。黄草笠白布直领澹黑带等说。终难从之。祝文措辞。来示似当。
一如亲丧。所后家祭。固不可不备礼行之。而服色极难便。凡主祀之人。或有故出他。则使子弟措辞代行。礼也。生亲丧期内。使子弟代行似好。玄石论此甚详。可考也。但所生亲期内。黄草笠白布直领澹黑带等说。终难从之。祝文措辞。来示似当。父妾之无子者不服缌。然庶母代母干家。嫡孙子女之被其养育者。则同爨之缌。正为此等设也。何可无三月之服。退溪稍加日数之说。礼无可据。何可以私意斟酌进退耶。庶孽服制。退溪虽言自度处之。若是无于礼之服。如何自度。庶母虽服轻。未葬之前。同气兄弟方累然而面垢。宴游等事不与之。似合人情。
当婚者期服未除。则古今论礼者。无可据之證。不可成婚。况祖父母正统之期。则其谨严又特异于旁期。虽有多少难便委折。期年内不可成婚。毋少放过宜矣。近来礼防大坏。祖父母期年。妻丧葬后。士夫之间。多行嫁娶。不可不慎。
答赵汝五(己巳)
国舅递迁云云。承悉之矣。是事前既详对。更无他议。而第 宗庙与文庙配享及国舅神主。 国典无迁不迁之槩见。到今亦可禀旨一定。而惜乎掌礼氏思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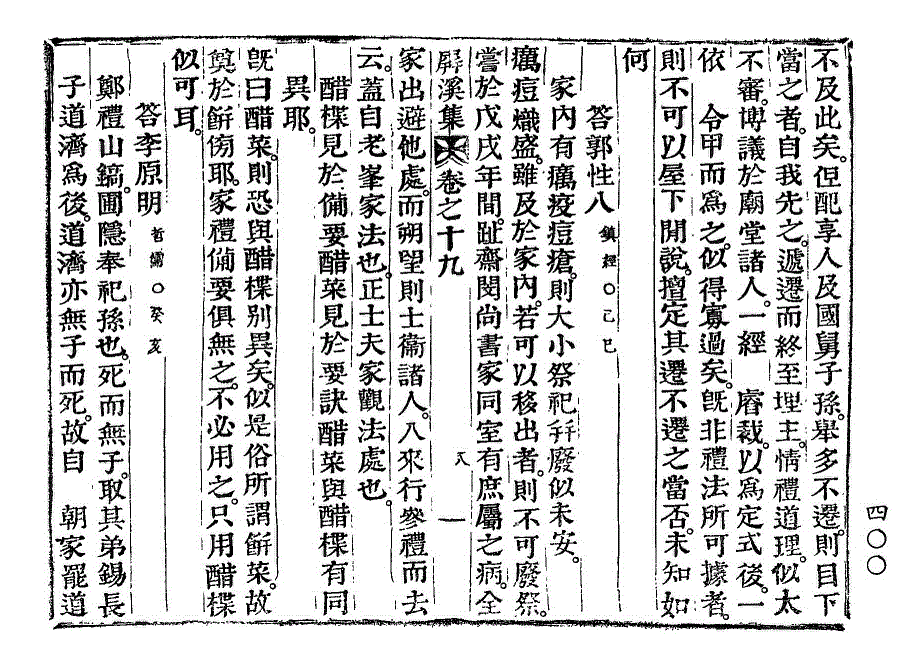 不及此矣。但配享人及国舅子孙。举多不迁。则目下当之者。自我先之。递迁而终至埋主。情礼道理。似太不审。博议于庙堂诸人。一经 睿裁。以为定式后。一依 令甲而为之。似得寡过矣。既非礼法所可据者。则不可以屋下閒说。擅定其迁不迁之当否。未知如何。
不及此矣。但配享人及国舅子孙。举多不迁。则目下当之者。自我先之。递迁而终至埋主。情礼道理。似太不审。博议于庙堂诸人。一经 睿裁。以为定式后。一依 令甲而为之。似得寡过矣。既非礼法所可据者。则不可以屋下閒说。擅定其迁不迁之当否。未知如何。答郭性八(镇经○己巳)
家内有疠疫痘疮。则大小祭祀并废似未安。
疠痘炽盛。虽及于家内。若可以移出者。则不可废祭。尝于戊戌年间。趾斋闵尚书家同室有庶属之病。全家出避他处。而朔望则士卫诸人。入来行参礼而去云。盖自老峰家法也。正士夫家观法处也。
醋楪见于备要。醋菜见于要诀。醋菜与醋楪有同异耶。
既曰醋菜。则恐与醋楪别异矣。似是俗所谓饼菜。故奠于饼傍耶。家礼备要俱无之。不必用之。只用醋楪似可耳。
答李原明(哲儒○癸亥)
郑礼山镐。圃隐奉祀孙也。死而无子。取其弟锡长子道济为后。道济亦无子而死。故自 朝家罢道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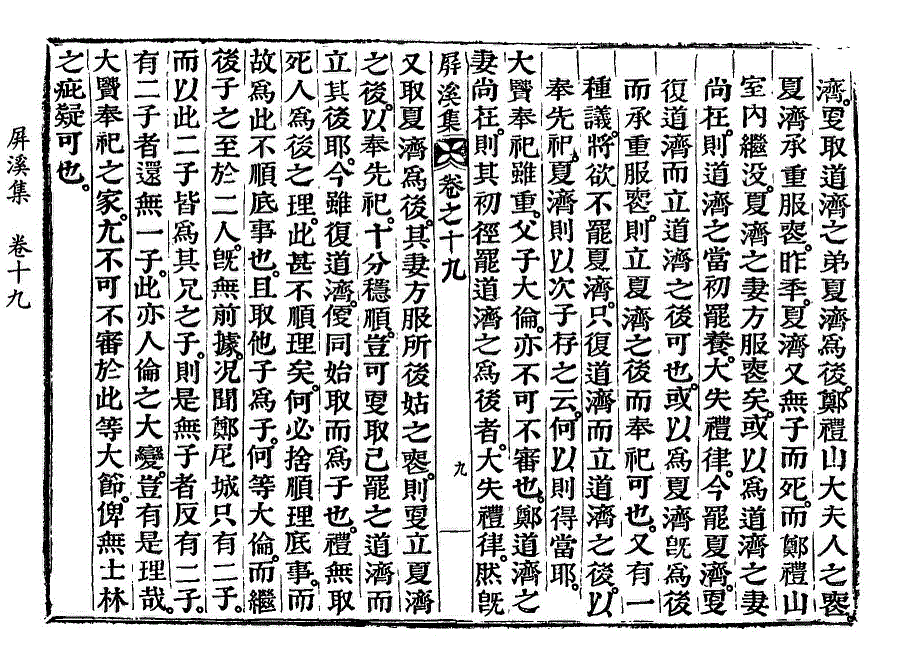 济。更取道济之弟夏济为后。郑礼山大夫人之丧。夏济承重服丧。昨年。夏济又无子而死。而郑礼山室内继没。夏济之妻方服丧矣。或以为道济之妻尚在。则道济之当初罢养。大失礼律。今罢夏济。更复道济而立道济之后可也。或以为夏济既为后而承重服丧。则立夏济之后而奉祀可也。又有一种议。将欲不罢夏济。只复道济而立道济之后。以奉先祀。夏济则以次子存之云。何以则得当耶。
济。更取道济之弟夏济为后。郑礼山大夫人之丧。夏济承重服丧。昨年。夏济又无子而死。而郑礼山室内继没。夏济之妻方服丧矣。或以为道济之妻尚在。则道济之当初罢养。大失礼律。今罢夏济。更复道济而立道济之后可也。或以为夏济既为后而承重服丧。则立夏济之后而奉祀可也。又有一种议。将欲不罢夏济。只复道济而立道济之后。以奉先祀。夏济则以次子存之云。何以则得当耶。大贤奉祀虽重。父子大伦。亦不可不审也。郑道济之妻尚在。则其初径罢道济之为后者。大失礼律。然既又取夏济为后。其妻方服所后姑之丧。则更立夏济之后。以奉先祀。十分稳顺。岂可更取已罢之道济而立其后耶。今虽复道济。便同始取而为子也。礼无取死人为后之理。此甚不顺理矣。何必舍顺理底事。而故为此不顺底事也。且取他子为子。何等大伦。而继后子之至于二人。既无前据。况闻郑尼城只有二子。而以此二子皆为其兄之子。则是无子者反有二子。有二子者还无一子。此亦人伦之大变。岂有是理哉。大贤奉祀之家。尤不可不审于此等大节。俾无士林之疵疑可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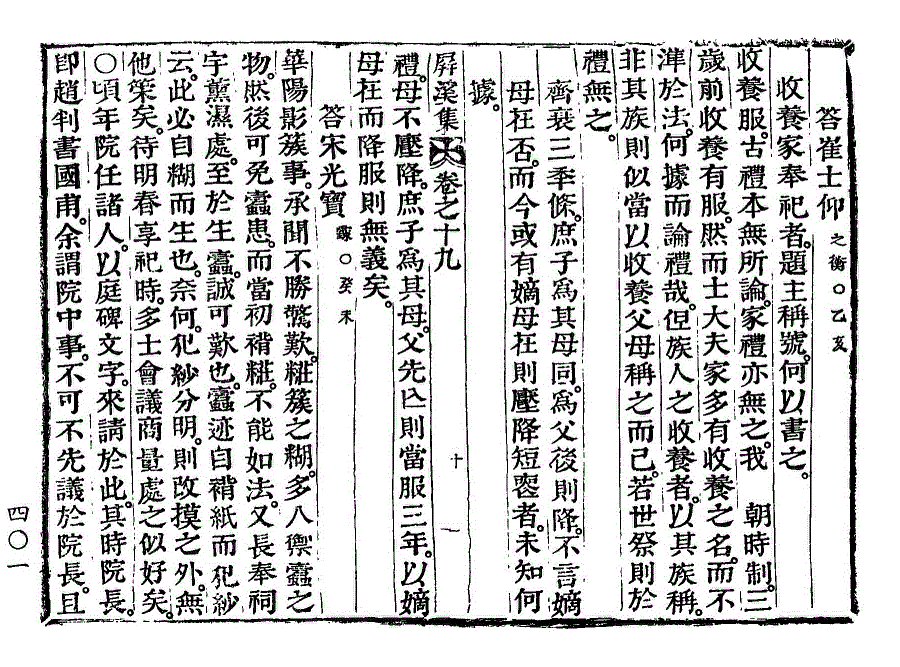 答崔士仰(之衡○乙亥)
答崔士仰(之衡○乙亥)收养家奉祀者。题主称号。何以书之。
收养服。古礼本无所论。家礼亦无之。我 朝时制。三岁前收养有服。然而士大夫家多有收养之名。而不准于法。何据而论礼哉。但族人之收养者。以其族称。非其族则似当以收养父母称之而已。若世祭则于礼无之。
齐衰三年条。庶子为其母同。为父后则降。不言嫡母在否。而今或有嫡母在则压降短丧者。未知何据。
礼。母不压降。庶子为其母。父先亡则当服三年。以嫡母在而降服则无义矣。
答宋光宝(
华阳影簇事。承闻不胜惊叹。妆簇之糊。多入御蠹之物。然后可免蠹患。而当初褙妆。不能如法。又长奉祠宇薰湿处。至于生蠹。诚可叹也。蠹迹自褙纸而犯纱云。此必自糊而生也。奈何。犯纱分明。则改摸之外。无他策矣。待明春享祀时。多士会议商量处之似好矣。○顷年院任诸人。以庭碑文字。来请于此。其时院长。即赵判书国甫。余谓院中事。不可不先议于院长。且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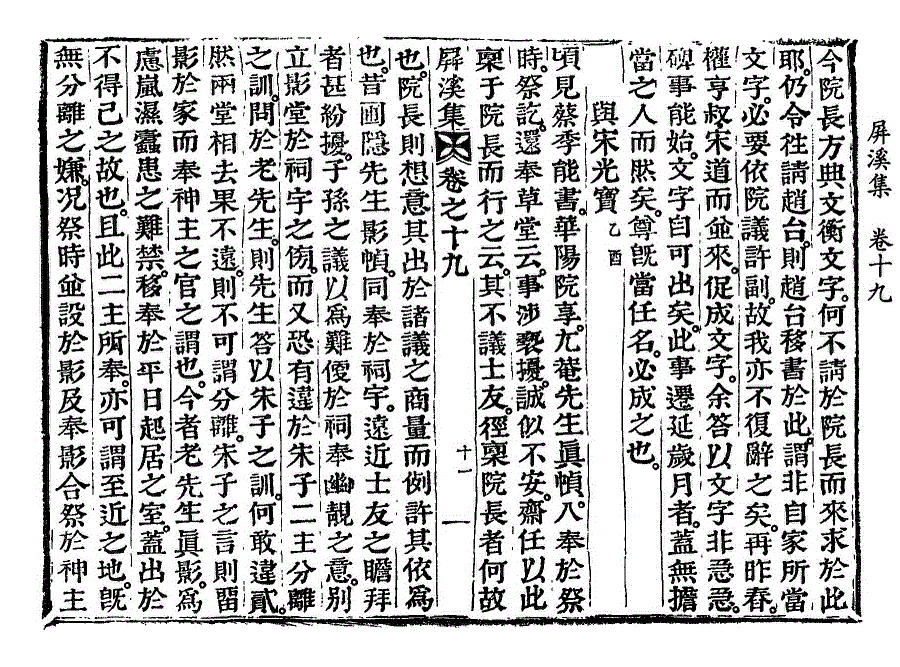 今院长方典文衡文字。何不请于院长而来求于此耶。仍令往请赵台。则赵台移书于此。谓非自家所当文字。必要依院议许副。故我亦不复辞之矣。再昨春。权亨叔,宋道而并来。促成文字。余答以文字非急急。碑事能始。文字自可出矣。此事迁延岁月者。盖无担当之人而然矣。尊既当任名。必成之也。
今院长方典文衡文字。何不请于院长而来求于此耶。仍令往请赵台。则赵台移书于此。谓非自家所当文字。必要依院议许副。故我亦不复辞之矣。再昨春。权亨叔,宋道而并来。促成文字。余答以文字非急急。碑事能始。文字自可出矣。此事迁延岁月者。盖无担当之人而然矣。尊既当任名。必成之也。与宋光宝(乙酉)
顷见蔡季能书。华阳院享。尤庵先生真帧。入奉于祭时。祭讫。还奉草堂云。事涉亵扰。诚似不安。斋任以此禀于院长而行之云。其不议士友。径禀院长者何故也。院长则想意其出于诸议之商量而例许其依为也。昔圃隐先生影帧。同奉于祠宇。远近士友之瞻拜者甚纷扰。子孙之议以为难便于祠奉幽靓之意。别立影堂于祠宇之傍。而又恐有违于朱子二主分离之训。问于老先生。则先生答以朱子之训。何敢违贰。然两堂相去果不远。则不可谓分离。朱子之言则留影于家而奉神主之官之谓也。今者老先生真影。为虑岚湿蠹患之难禁。移奉于平日起居之室。盖出于不得已之故也。且此二主所奉。亦可谓至近之地。既无分离之嫌。况祭时并设于影及奉影合祭于神主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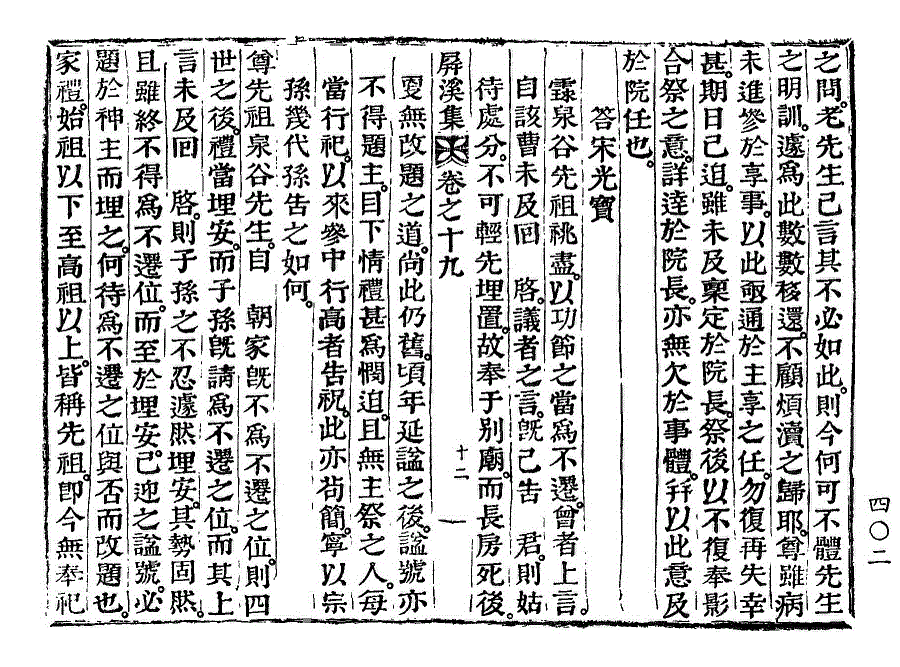 之问。老先生已言其不必如此。则今何可不体先生之明训。遽为此数数移还。不顾烦渎之归耶。尊虽病未进参于享事。以此亟通于主享之任。勿复再失幸甚。期日已迫。虽未及禀定于院长。祭后以不复奉影合祭之意。详达于院长。亦无欠于事体。并以此意及于院任也。
之问。老先生已言其不必如此。则今何可不体先生之明训。遽为此数数移还。不顾烦渎之归耶。尊虽病未进参于享事。以此亟通于主享之任。勿复再失幸甚。期日已迫。虽未及禀定于院长。祭后以不复奉影合祭之意。详达于院长。亦无欠于事体。并以此意及于院任也。答宋光宝
■(雨球)泉谷先祖祧尽。以功节之当为不迁。曾者上言。自该曹未及回 启。议者之言。既已告 君。则姑待处分。不可轻先埋置。故奉于别庙。而长房死后。更无改题之道。尚此仍旧。顷年延谥之后。谥号亦不得题主。目下情礼甚为悯迫。且无主祭之人。每当行祀。以来参中行高者告祝。此亦苟简。宁以宗孙几代孙告之如何。
尊先祖泉谷先生。自 朝家既不为不迁之位。则四世之后。礼当埋安。而子孙既请为不迁之位。而其上言未及回 启。则子孙之不忍遽然埋安。其势固然。且虽终不得为不迁位。而至于埋安。已迎之谥号。必题于神主而埋之。何待为不迁之位与否而改题也。家礼。始祖以下至高祖以上。皆称先祖。即今无奉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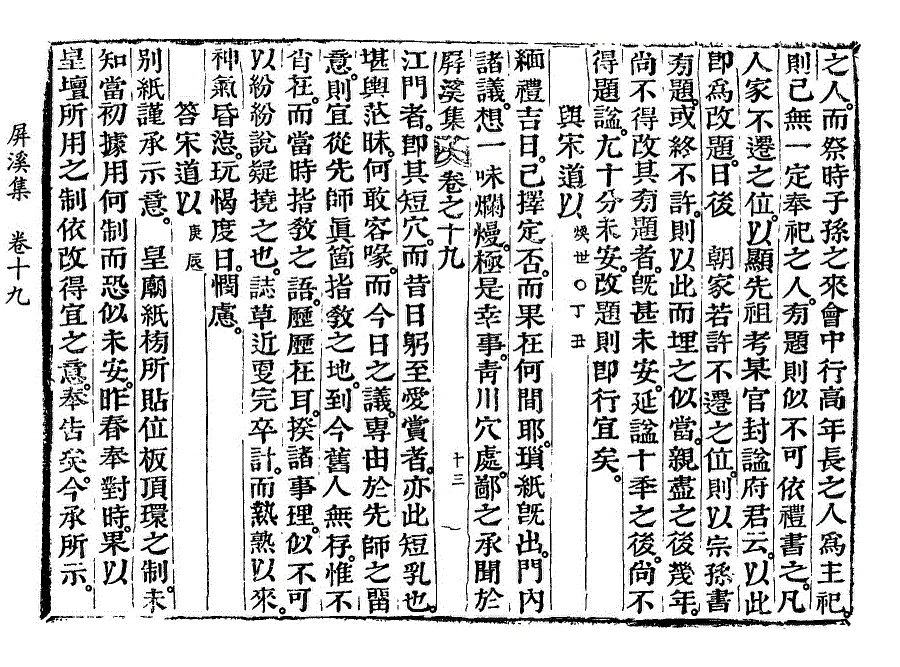 之人。而祭时子孙之来会中行高年长之人为主祀。则已无一定奉祀之人。旁题则似不可依礼书之。凡人家不迁之位。以显先祖考某官封谥府君云。以此即为改题。日后 朝家若许不迁之位。则以宗孙书旁题。或终不许。则以此而埋之似当。亲尽之后几年。尚不得改其旁题者。既甚未安。延谥十年之后。尚不得题谥。尤十分未安。改题则即行宜矣。
之人。而祭时子孙之来会中行高年长之人为主祀。则已无一定奉祀之人。旁题则似不可依礼书之。凡人家不迁之位。以显先祖考某官封谥府君云。以此即为改题。日后 朝家若许不迁之位。则以宗孙书旁题。或终不许。则以此而埋之似当。亲尽之后几年。尚不得改其旁题者。既甚未安。延谥十年之后。尚不得题谥。尤十分未安。改题则即行宜矣。与宋道以(焕世○丁丑)
缅礼吉日。已择定否。而果在何间耶。琐纸既出。门内诸议。想一味烂熳。极是幸事。青川穴处。鄙之承闻于江门者。即其短穴。而昔日躬至爱赏者。亦此短乳也。堪舆茫昧。何敢容喙。而今日之议。专由于先师之留意。则宜从先师真个指教之地。到今旧人无存。惟不肖在。而当时指教之语。历历在耳。揆诸事理。似不可以纷纷说疑挠之也。志草近更完卒计。而热熟以来。神气昏惉。玩愒度日。悯虑。
答宋道以(庚辰)
别纸谨承示意。 皇庙纸榜所贴位板顶环之制。未知当初据用何制而恐似未安。昨春奉对时。果以 皇坛所用之制依改得宜之意。奉告矣。今承所示。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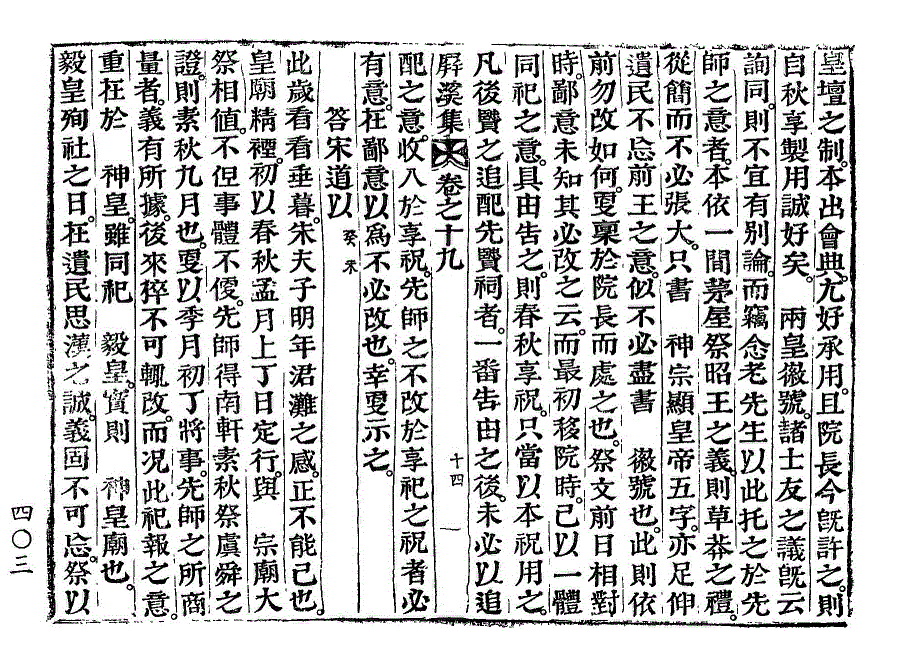 皇坛之制。本出会典。尤好承用。且院长今既许之。则自秋享制用诚好矣。 两皇徽号。诸士友之议既云询同。则不宜有别论。而窃念老先生以此托之于先师之意者。本依一间茅屋祭昭王之义。则草莽之礼。从简而不必张大。只书 神宗显皇帝五字。亦足伸遗民不忘前王之意。似不必尽书 徽号也。此则依前勿改如何。更禀于院长而处之也。祭文前日相对时。鄙意未知其必改之云。而最初移院时。已以一体同祀之意。具由告之。则春秋享祝。只当以本祝用之。凡后贤之追配先贤祠者。一番告由之后。未必以追配之意。收入于享祝。先师之不改于享祀之祝者必有意。在鄙意以为不必改也。幸更示之。
皇坛之制。本出会典。尤好承用。且院长今既许之。则自秋享制用诚好矣。 两皇徽号。诸士友之议既云询同。则不宜有别论。而窃念老先生以此托之于先师之意者。本依一间茅屋祭昭王之义。则草莽之礼。从简而不必张大。只书 神宗显皇帝五字。亦足伸遗民不忘前王之意。似不必尽书 徽号也。此则依前勿改如何。更禀于院长而处之也。祭文前日相对时。鄙意未知其必改之云。而最初移院时。已以一体同祀之意。具由告之。则春秋享祝。只当以本祝用之。凡后贤之追配先贤祠者。一番告由之后。未必以追配之意。收入于享祝。先师之不改于享祀之祝者必有意。在鄙意以为不必改也。幸更示之。答宋道以(癸未)
此岁看看垂暮。朱夫子明年涒滩之感。正不能已也。皇庙精禋。初以春秋孟月上丁日定行。与 宗庙大祭相值。不但事体不便。先师得南轩素秋祭虞舜之證。则素秋九月也。更以季月初丁将事。先师之所商量者。义有所据。后来猝不可辄改。而况此祀报之意。重在于 神皇。虽同祀 毅皇。实则 神皇庙也。 毅皇殉社之日。在遗民思汉之诚。义固不可忘。祭以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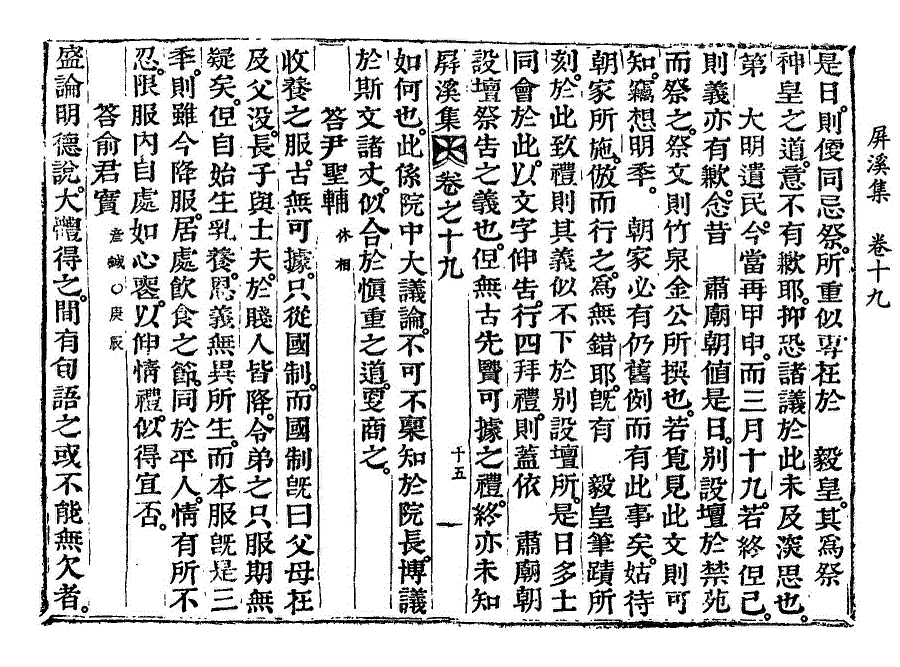 是日。则便同忌祭。所重似专在于 毅皇。其为祭 神皇之道。意不有歉耶。抑恐诸议于此未及深思也。第 大明遗民。今当再甲申。而三月十九。若终但已。则义亦有歉。念昔 肃庙朝值是日。别设坛于禁苑而祭之。祭文则竹泉金公所撰也。若觅见此文则可知。窃想明年。 朝家必有仍旧例而有此事矣。姑待朝家所施。仿而行之。为无错耶。既有 毅皇笔迹所刻。于此致礼则其义似不下于别设坛所。是日多士同会于此。以文字伸告。行四拜礼。则盖依 肃庙朝设坛祭告之义也。但无古先贤可据之礼。终亦未知如何也。此系院中大议论。不可不禀知于院长。博议于斯文诸丈。似合于慎重之道。更商之。
是日。则便同忌祭。所重似专在于 毅皇。其为祭 神皇之道。意不有歉耶。抑恐诸议于此未及深思也。第 大明遗民。今当再甲申。而三月十九。若终但已。则义亦有歉。念昔 肃庙朝值是日。别设坛于禁苑而祭之。祭文则竹泉金公所撰也。若觅见此文则可知。窃想明年。 朝家必有仍旧例而有此事矣。姑待朝家所施。仿而行之。为无错耶。既有 毅皇笔迹所刻。于此致礼则其义似不下于别设坛所。是日多士同会于此。以文字伸告。行四拜礼。则盖依 肃庙朝设坛祭告之义也。但无古先贤可据之礼。终亦未知如何也。此系院中大议论。不可不禀知于院长。博议于斯文诸丈。似合于慎重之道。更商之。答尹圣辅(休相)
收养之服。古无可据。只从国制。而国制既曰父母在及父没。长子与士夫。于贱人皆降。令弟之只服期无疑矣。但自始生乳养。恩义无异所生。而本服既是三年。则虽今降服。居处饮食之节。同于平人。情有所不忍。限服内自处如心丧。以伸情礼。似得宜否。
答俞君实(彦诚○庚辰)
盛论明德说。大体得之。间有句语之或不能无欠者。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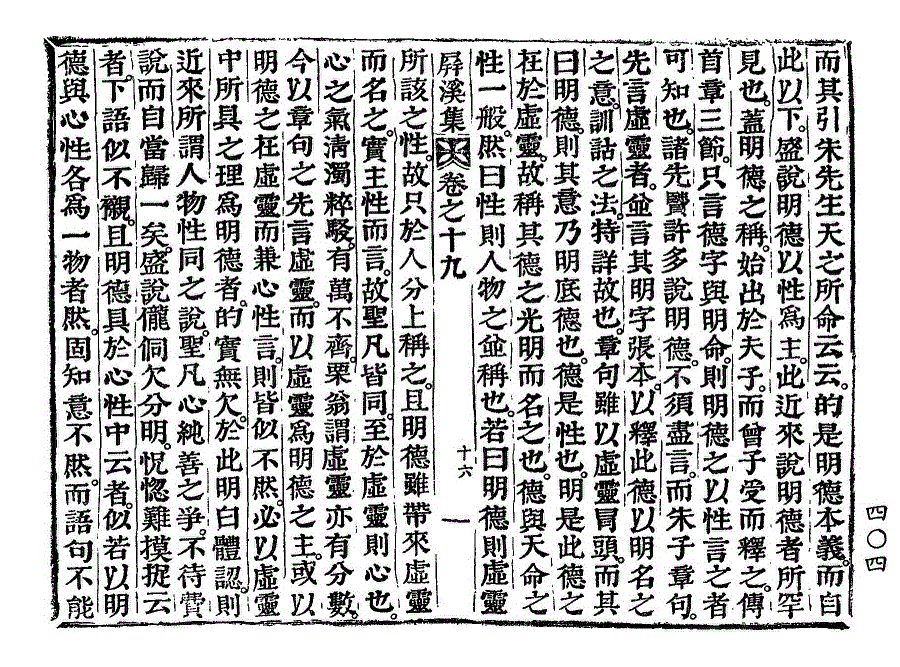 而其引朱先生天之所命云云。的是明德本义。而自此以下。盛说明德以性为主。此近来说明德者所罕见也。盖明德之称。始出于夫子。而曾子受而释之。传首章三节。只言德字与明命。则明德之以性言之者可知也。诸先贤许多说明德。不须尽言。而朱子章句。先言虚灵者。并言其明字张本。以释此德以明名之之意。训诂之法。特详故也。章句虽以虚灵冒头。而其曰明德。则其意乃明底德也。德是性也。明是此德之在于虚灵。故称其德之光明而名之也。德与天命之性一般。然曰性则人物之并称也。若曰明德则虚灵所该之性。故只于人分上称之。且明德虽带来虚灵而名之。实主性而言。故圣凡皆同。至于虚灵则心也。心之气清浊粹驳。有万不齐。栗翁谓虚灵亦有分数。今以章句之先言虚灵。而以虚灵为明德之主。或以明德之在虚灵而兼心性言。则皆似不然。必以虚灵中所具之理为明德者。的实无欠。于此明白体认。则近来所谓人物性同之说。圣凡心纯善之争。不待费说而自当归一矣。盛说儱侗欠分明。恍惚难摸捉云者。下语似不衬。且明德具于心性中云者。似若以明德与心性各为一物者然。固知意不然。而语句不能
而其引朱先生天之所命云云。的是明德本义。而自此以下。盛说明德以性为主。此近来说明德者所罕见也。盖明德之称。始出于夫子。而曾子受而释之。传首章三节。只言德字与明命。则明德之以性言之者可知也。诸先贤许多说明德。不须尽言。而朱子章句。先言虚灵者。并言其明字张本。以释此德以明名之之意。训诂之法。特详故也。章句虽以虚灵冒头。而其曰明德。则其意乃明底德也。德是性也。明是此德之在于虚灵。故称其德之光明而名之也。德与天命之性一般。然曰性则人物之并称也。若曰明德则虚灵所该之性。故只于人分上称之。且明德虽带来虚灵而名之。实主性而言。故圣凡皆同。至于虚灵则心也。心之气清浊粹驳。有万不齐。栗翁谓虚灵亦有分数。今以章句之先言虚灵。而以虚灵为明德之主。或以明德之在虚灵而兼心性言。则皆似不然。必以虚灵中所具之理为明德者。的实无欠。于此明白体认。则近来所谓人物性同之说。圣凡心纯善之争。不待费说而自当归一矣。盛说儱侗欠分明。恍惚难摸捉云者。下语似不衬。且明德具于心性中云者。似若以明德与心性各为一物者然。固知意不然。而语句不能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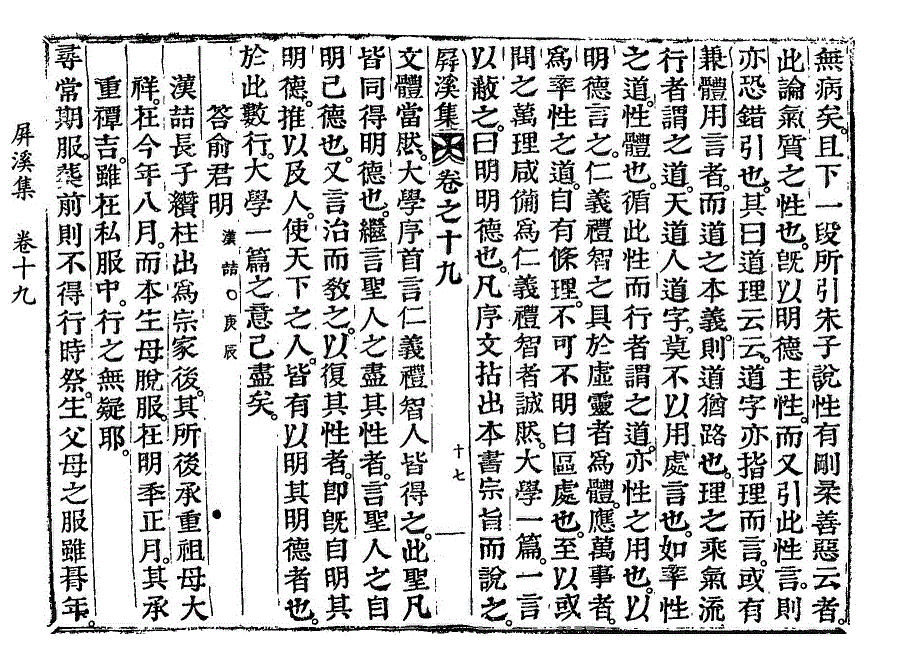 无病矣。且下一段所引朱子说性有刚柔善恶云者。此论气质之性也。既以明德主性。而又引此性言。则亦恐错引也。其曰道理云云。道字亦指理而言。或有兼体用言者。而道之本义。则道犹路也。理之乘气流行者谓之道。天道人道字。莫不以用处言也。如率性之道。性体也。循此性而行者谓之道。亦性之用也。以明德言之。仁义礼智之具于虚灵者为体。应万事者。为率性之道。自有条理。不可不明白区处也。至以或问之万理咸备为仁义礼智者诚然。大学一篇。一言以蔽之。曰明明德也。凡序文拈出本书宗旨而说之。文体当然。大学序首言仁义礼智人皆得之。此圣凡皆同得明德也。继言圣人之尽其性者。言圣人之自明己德也。又言治而教之。以复其性者。即既自明其明德。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也。于此数行。大学一篇之意已尽矣。
无病矣。且下一段所引朱子说性有刚柔善恶云者。此论气质之性也。既以明德主性。而又引此性言。则亦恐错引也。其曰道理云云。道字亦指理而言。或有兼体用言者。而道之本义。则道犹路也。理之乘气流行者谓之道。天道人道字。莫不以用处言也。如率性之道。性体也。循此性而行者谓之道。亦性之用也。以明德言之。仁义礼智之具于虚灵者为体。应万事者。为率性之道。自有条理。不可不明白区处也。至以或问之万理咸备为仁义礼智者诚然。大学一篇。一言以蔽之。曰明明德也。凡序文拈出本书宗旨而说之。文体当然。大学序首言仁义礼智人皆得之。此圣凡皆同得明德也。继言圣人之尽其性者。言圣人之自明己德也。又言治而教之。以复其性者。即既自明其明德。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也。于此数行。大学一篇之意已尽矣。答俞君明(汉哲○庚辰)
汉哲长子缵柱出为宗家后。其所后承重祖母大祥。在今年八月。而本生母脱服。在明年正月。其承重禫吉。虽在私服中。行之无疑耶。
寻常期服。葬前则不得行时祭。生父母之服虽期年。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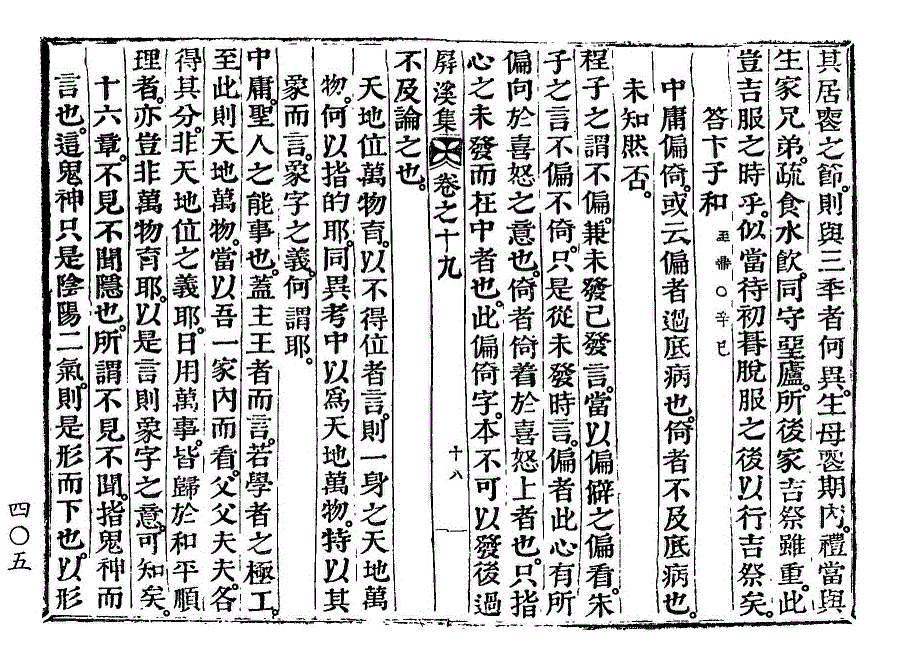 其居丧之节。则与三年者何异。生母丧期内。礼当与生家兄弟。疏食水饮。同守垩庐。所后家吉祭虽重。此岂吉服之时乎。似当待初期脱服之后以行吉祭矣。
其居丧之节。则与三年者何异。生母丧期内。礼当与生家兄弟。疏食水饮。同守垩庐。所后家吉祭虽重。此岂吉服之时乎。似当待初期脱服之后以行吉祭矣。答卞子和(至鼎○辛巳)
中庸偏倚。或云偏者过底病也。倚者不及底病也。未知然否。
程子之谓不偏。兼未发已发言。当以偏僻之偏看。朱子之言不偏不倚。只是从未发时言。偏者此心有所偏向于喜怒之意也。倚者倚着于喜怒上者也。只指心之未发而在中者也。此偏倚字。本不可以发后过不及论之也。
天地位万物育。以不得位者言。则一身之天地万物。何以指的耶。同异考中以为天地万物。特以其象而言。象字之义。何谓耶。
中庸。圣人之能事也。盖主王者而言。若学者之极工。至此则天地万物。当以吾一家内而看。父父夫夫。各得其分。非天地位之义耶。日用万事。皆归于和平顺理者。亦岂非万物育耶。以是言则象字之意。可知矣。
十六章。不见不闻隐也。所谓不见不闻。指鬼神而言也。这鬼神只是阴阳二气。则是形而下也。以形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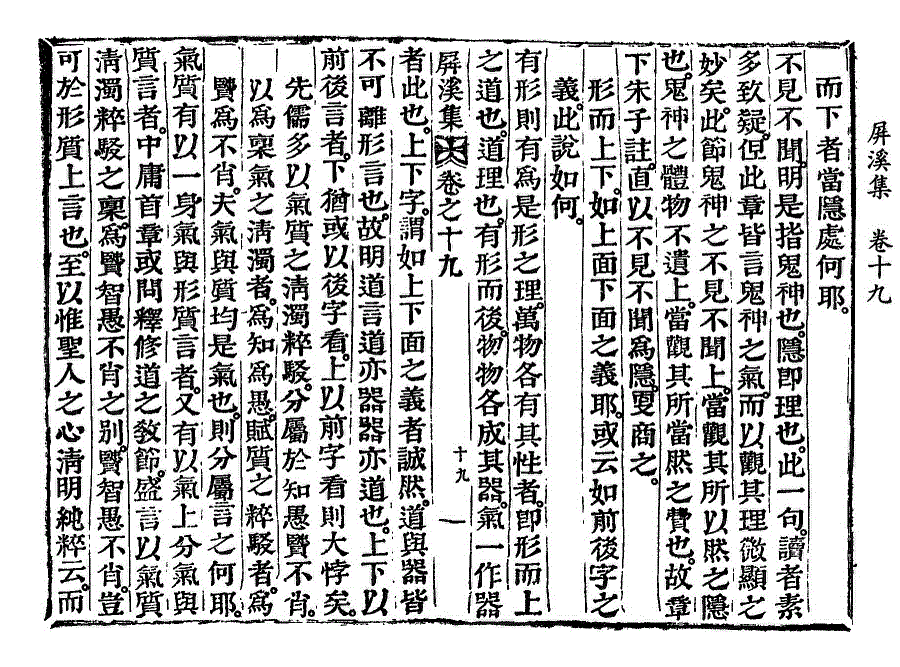 而下者当隐处何耶。
而下者当隐处何耶。不见不闻。明是指鬼神也。隐即理也。此一句。读者素多致疑。但此章皆言鬼神之气。而以观其理微显之妙矣。此节鬼神之不见不闻上。当观其所以然之隐也。鬼神之体物不遗上。当观其所当然之费也。故章下朱子注。直以不见不闻为隐。更商之。
形而上下。如上面下面之义耶。或云如前后字之义。此说如何。
有形则有为是形之理。万物各有其性者。即形而上之道也。道理也。有形而后。物物各成其器。气一作器者此也。上下字。谓如上下面之义者诚然。道与器皆不可离形言也。故明道言道亦器器亦道也。上下以前后言者。下犹或以后字看。上以前字看则大悖矣。
先儒多以气质之清浊粹驳。分属于知愚贤不肖。以为禀气之清浊者。为知为愚。赋质之粹驳者。为贤为不肖。夫气与质均是气也。则分属言之何耶。
气质有以一身气与形质言者。又有以气上分气与质言者。中庸首章或问释修道之教节。盛言以气质清浊粹驳之禀。为贤智愚不肖之别。贤智愚不肖。岂可于形质上言也。至以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云。而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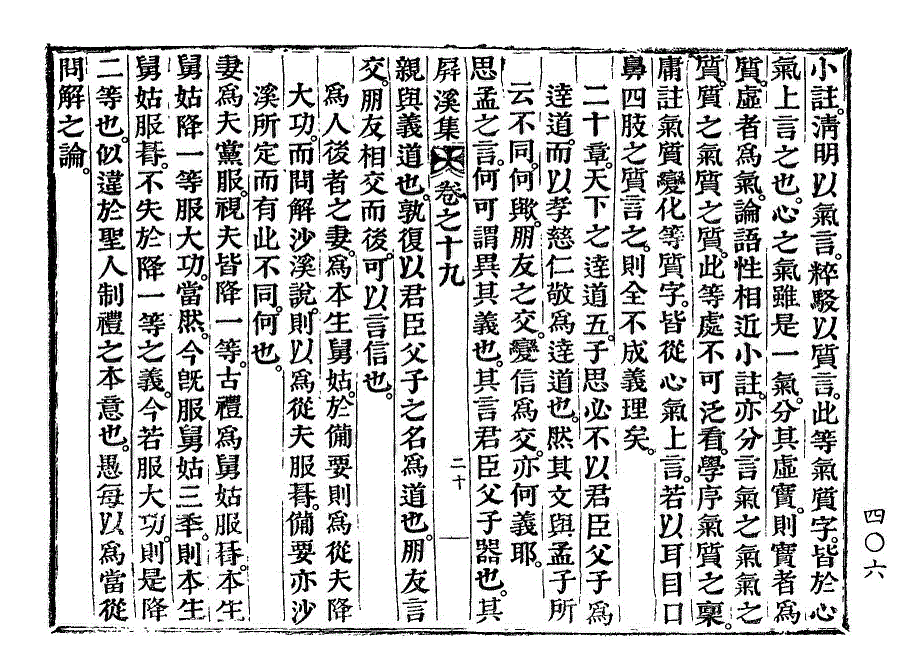 小注。清明以气言。粹驳以质言。此等气质字。皆于心气上言之也。心之气虽是一气。分其虚实。则实者为质。虚者为气。论语性相近小注。亦分言气之气气之质。质之气质之质。此等处不可泛看。学序气质之禀。庸注气质变化等质字。皆从心气上言。若以耳目口鼻四肢之质言之。则全不成义理矣。
小注。清明以气言。粹驳以质言。此等气质字。皆于心气上言之也。心之气虽是一气。分其虚实。则实者为质。虚者为气。论语性相近小注。亦分言气之气气之质。质之气质之质。此等处不可泛看。学序气质之禀。庸注气质变化等质字。皆从心气上言。若以耳目口鼻四肢之质言之。则全不成义理矣。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子思必不以君臣父子为达道。而以孝慈仁敬为达道也。然其文与孟子所云不同。何欤。朋友之交。变信为交。亦何义耶。
思孟之言。何可谓异其义也。其言君臣父子器也。其亲与义道也。孰复以君臣父子之名为道也。朋友言交。朋友相交而后。可以言信也。
为人后者之妻。为本生舅姑。于备要则为从夫降大功。而问解沙溪说。则以为从夫服期。备要亦沙溪所定而有此不同。何也。
妻为夫党服。视夫皆降一等。古礼为舅姑服期。本生舅姑降一等服大功。当然。今既服舅姑三年。则本生舅姑服期。不失于降一等之义。今若服大功。则是降二等也。似违于圣人制礼之本意也。愚每以为当从问解之论。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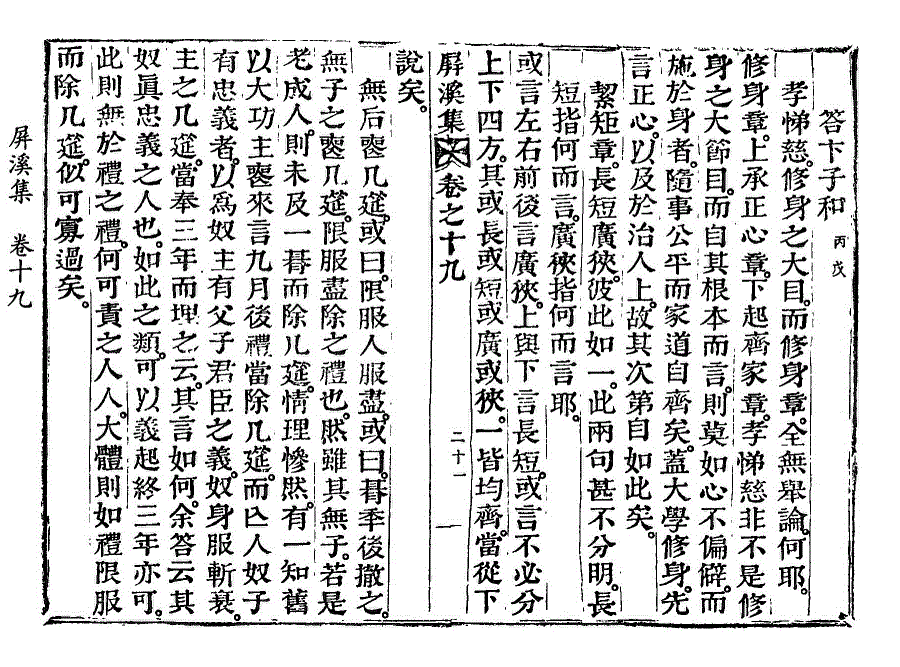 答卞子和(丙戌)
答卞子和(丙戌)孝悌慈。修身之大目。而修身章。全无举论。何耶。
修身章。上承正心章。下起齐家章。孝悌慈非不是修身之大节目。而自其根本而言。则莫如心不偏僻。而施于身者。随事公平而家道自齐矣。盖大学修身。先言正心。以及于治人上。故其次第自如此矣。
絜矩章。长短广狭。彼此如一。此两句甚不分明。长短指何而言。广狭指何而言耶。
或言左右前后言广狭。上与下言长短。或言不必分上下四方。其或长或短或广或狭。一皆均齐。当从下说矣。
无后丧几筵。或曰。限服人服尽。或曰。期年后撤之。
无子之丧几筵。限服尽除之礼也。然虽其无子。若是老成人。则未及一期而除几筵。情理惨然。有一知旧以大功主丧来言九月后礼当除几筵。而亡人奴子有忠义者。以为奴主有父子君臣之义。奴身服斩衰。主之几筵。当奉三年而埋之云。其言如何。余答云其奴真忠义之人也。如此之类。可以义起终三年亦可。此则无于礼之礼。何可责之人人。大体则如礼限服而除几筵。似可寡过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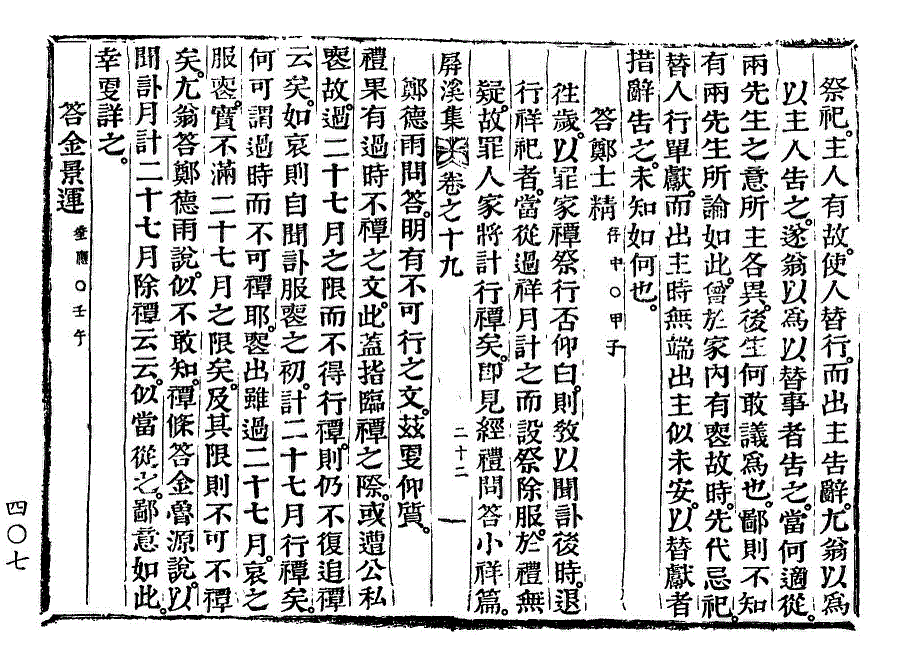 祭祀。主人有故。使人替行。而出主告辞。尤翁以为以主人告之。遂翁以为以替事者告之。当何适从。
祭祀。主人有故。使人替行。而出主告辞。尤翁以为以主人告之。遂翁以为以替事者告之。当何适从。两先生之意所主各异。后生何敢议为也。鄙则不知有两先生所论如此。曾于家内有丧故时。先代忌祀。替人行单献。而出主时无端出主似未安。以替献者措辞告之。未知如何也。
答郑士精(存中○甲子)
往岁。以罪家禫祭行否仰白。则教以闻讣后时。退行祥祀者。当从过祥月计之而设祭除服。于礼无疑。故罪人家将计行禫矣。即见经礼问答小祥篇。郑德雨问答。明有不可行之文。兹更仰质。
礼果有过时不禫之文。此盖指临禫之际。或遭公私丧故。过二十七月之限而不得行禫。则仍不复追禫云矣。如哀则自闻讣服丧之初。计二十七月行禫矣。何可谓过时而不可禫耶。丧出虽过二十七月。哀之服丧。实不满二十七月之限矣。及其限则不可不禫矣。尤翁答郑德雨说。似不敢知。禫条答金鲁源说。以闻讣月计二十七月除禫云云。似当从之。鄙意如此。幸更详之。
答金景运(奎应○壬午)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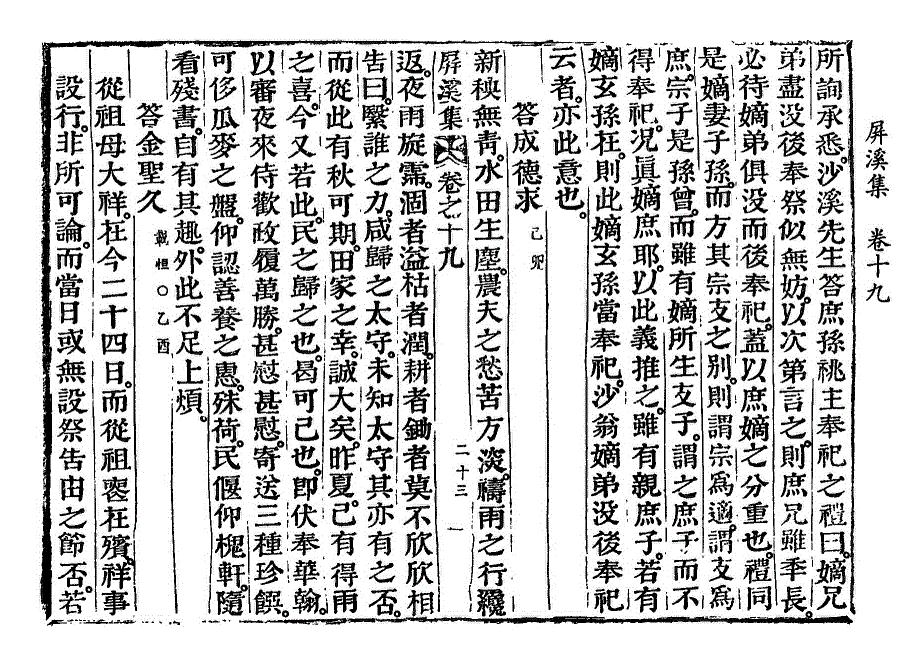 所询承悉。沙溪先生答庶孙祧主奉祀之礼曰。嫡兄弟尽没后奉祭似无妨。以次第言之。则庶兄虽年长。必待嫡弟俱没而后奉祀。盖以庶嫡之分重也。礼同是嫡妻子孙。而方其宗支之别。则谓宗为适。谓支为庶。宗子是孙曾。而虽有嫡所生支子。谓之庶子而不得奉祀。况真嫡庶耶。以此义推之。虽有亲庶子。若有嫡玄孙在。则此嫡玄孙当奉祀。沙翁嫡弟没后奉祀云者。亦此意也。
所询承悉。沙溪先生答庶孙祧主奉祀之礼曰。嫡兄弟尽没后奉祭似无妨。以次第言之。则庶兄虽年长。必待嫡弟俱没而后奉祀。盖以庶嫡之分重也。礼同是嫡妻子孙。而方其宗支之别。则谓宗为适。谓支为庶。宗子是孙曾。而虽有嫡所生支子。谓之庶子而不得奉祀。况真嫡庶耶。以此义推之。虽有亲庶子。若有嫡玄孙在。则此嫡玄孙当奉祀。沙翁嫡弟没后奉祀云者。亦此意也。答成德求(己卯)
新秧无青。水田生尘。农夫之愁苦方深。祷雨之行才返。夜雨旋霈。涸者溢枯者润。耕者锄者莫不欣欣相告曰。繄谁之力。咸归之太守。未知太守其亦有之否。而从此有秋可期。田家之幸。诚大矣。昨夏。已有得雨之喜。今又若此。民之归之也。曷可已也。即伏奉华翰。以审夜来侍欢政履万胜。甚慰甚慰。寄送三种珍馔。可侈瓜麦之盘。仰认善养之惠。殊荷。民偃仰槐轩。随看残书。自有其趣。外此不足上烦。
答金圣久(载恒○乙酉)
从祖母大祥。在今二十四日。而从祖丧在殡。祥事设行。非所可论。而当日或无设祭告由之节否。若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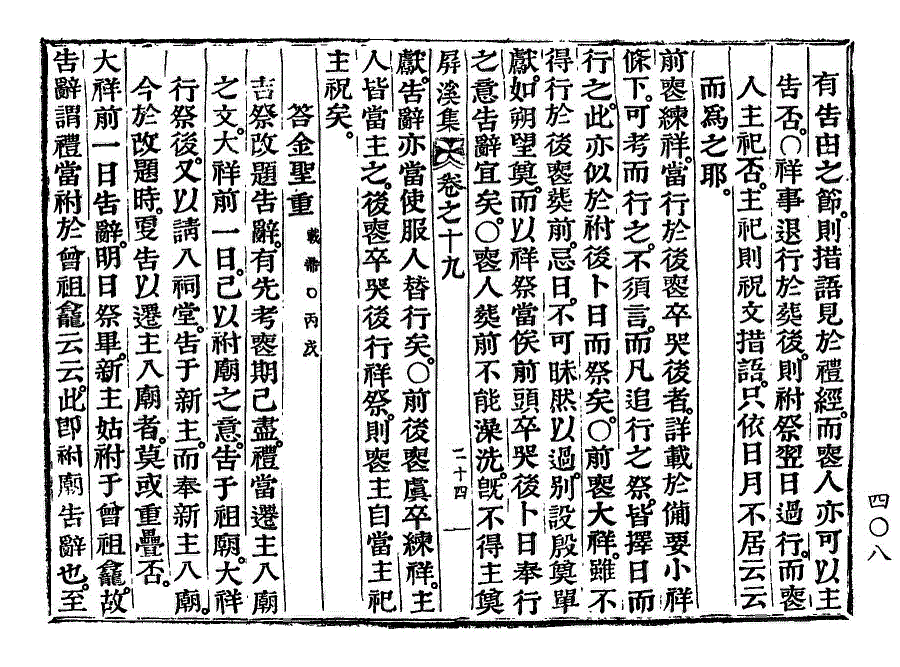 有告由之节。则措语见于礼经。而丧人亦可以主告否。○祥事退行于葬后。则祔祭翌日过行。而丧人主祀否。主祀则祝文措语。只依日月不居云云而为之耶。
有告由之节。则措语见于礼经。而丧人亦可以主告否。○祥事退行于葬后。则祔祭翌日过行。而丧人主祀否。主祀则祝文措语。只依日月不居云云而为之耶。前丧练祥。当行于后丧卒哭后者。详载于备要小祥条下。可考而行之。不须言。而凡追行之祭。皆择日而行之。此亦似于祔后卜日而祭矣。○前丧大祥。虽不得行于后丧葬前。忌日。不可昧然以过。别设殷奠单献。如朔望奠。而以祥祭当俟前头卒哭后卜日奉行之意告辞宜矣。○丧人葬前不能澡洗。既不得主奠献。告辞亦当使服人替行矣。○前后丧虞卒练祥。主人皆当主之。后丧卒哭后行祥祭。则丧主自当主祀主祝矣。
答金圣重(载鼎○丙戌)
吉祭改题告辞。有先考丧期已尽。礼当迁主入庙之文。大祥前一日。已以祔庙之意。告于祖庙。大祥行祭后。又以请入祠堂。告于新主。而奉新主入庙。今于改题时。更告以迁主入庙者。莫或重叠否。
大祥前一日告辞。明日祭毕。新主姑祔于曾祖龛。故告辞谓礼当祔于曾祖龛云云。此即祔庙告辞也。至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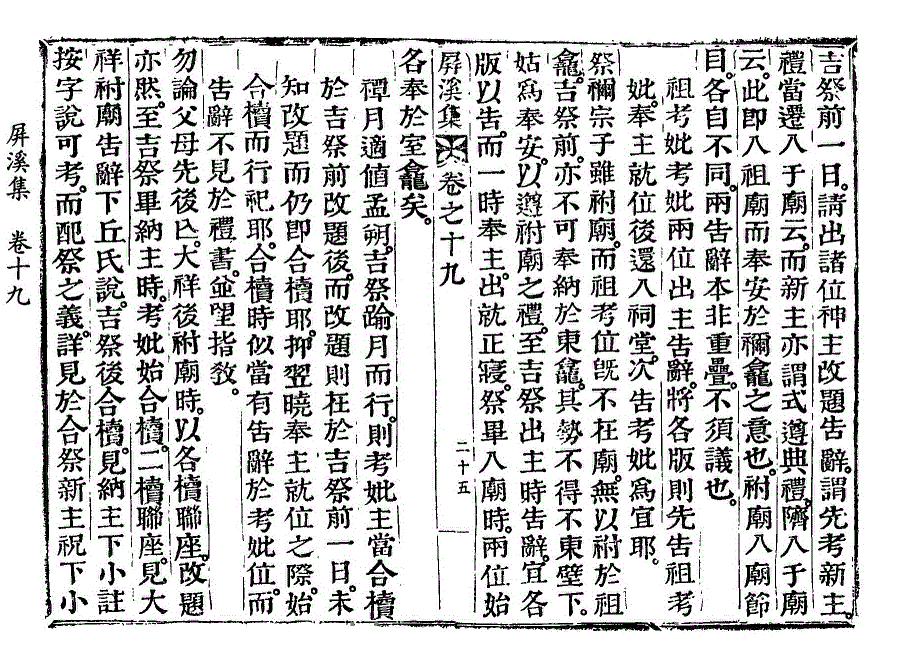 吉祭前一日。请出诸位神主改题告辞。谓先考新主。礼当迁入于庙云。而新主亦谓式遵典礼。隮入于庙云。此即入祖庙而奉安于祢龛之意也。祔庙入庙节目。各自不同。两告辞本非重叠。不须议也。
吉祭前一日。请出诸位神主改题告辞。谓先考新主。礼当迁入于庙云。而新主亦谓式遵典礼。隮入于庙云。此即入祖庙而奉安于祢龛之意也。祔庙入庙节目。各自不同。两告辞本非重叠。不须议也。祖考妣考妣两位出主告辞。将各版则先告祖考妣。奉主就位后还入祠堂。次告考妣为宜耶。
祭祢宗子虽祔庙。而祖考位既不在庙。无以祔于祖龛。吉祭前。亦不可奉纳于东龛。其势不得不东壁下。姑为奉安。以遵祔庙之礼。至吉祭出主时告辞。宜各版以告。而一时奉主。出就正寝。祭毕入庙时。两位始各奉于室龛矣。
禫月适值孟朔。吉祭踰月而行。则考妣主当合椟于吉祭前改题后。而改题则在于吉祭前一日。未知改题而仍即合椟耶。抑翌晓奉主就位之际。始合椟而行祀耶。合椟时似当有告辞于考妣位。而告辞不见于礼书。并望指教。
勿论父母先后亡。大祥后祔庙时。以各椟联座。改题亦然。至吉祭毕纳主时。考妣始合椟。二椟联座。见大祥祔庙告辞下丘氏说。吉祭后合椟。见纳主下小注按字说可考。而配祭之义。详见于合祭新主祝下小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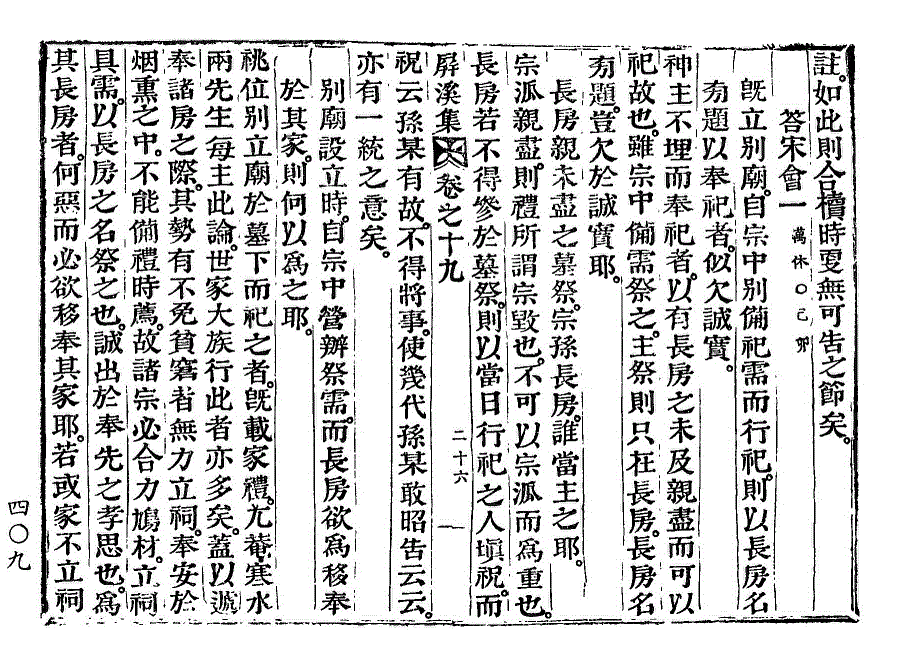 注。如此则合椟时更无可告之节矣。
注。如此则合椟时更无可告之节矣。答宋会一(万休○己卯)
既立别庙。自宗中别备祀需而行祀。则以长房名旁题以奉祀者。似欠诚实。
神主不埋而奉祀者。以有长房之未及亲尽而可以祀故也。虽宗中备需祭之。主祭则只在长房。长房名旁题。岂欠于诚实耶。
长房亲未尽之墓祭。宗孙长房。谁当主之耶。
宗派亲尽。则礼所谓宗毁也。不可以宗派而为重也。长房若不得参于墓祭。则以当日行祀之人填祝。而祝云孙某有故。不得将事。使几代孙某敢昭告云云。亦有一统之意矣。
别庙设立时。自宗中营办祭需。而长房欲为移奉于其家。则何以为之耶。
祧位别立庙于墓下而祀之者。既载家礼。尤庵,寒水两先生每主此论。世家大族行此者亦多矣。盖以递奉诸房之际。其势有不免贫窘者无力立祠。奉安于烟熏之中。不能备礼时荐。故诸宗必合力鸠材。立祠具需。以长房之名祭之也。诚出于奉先之孝思也。为其长房者。何恶而必欲移奉其家耶。若或家不立祠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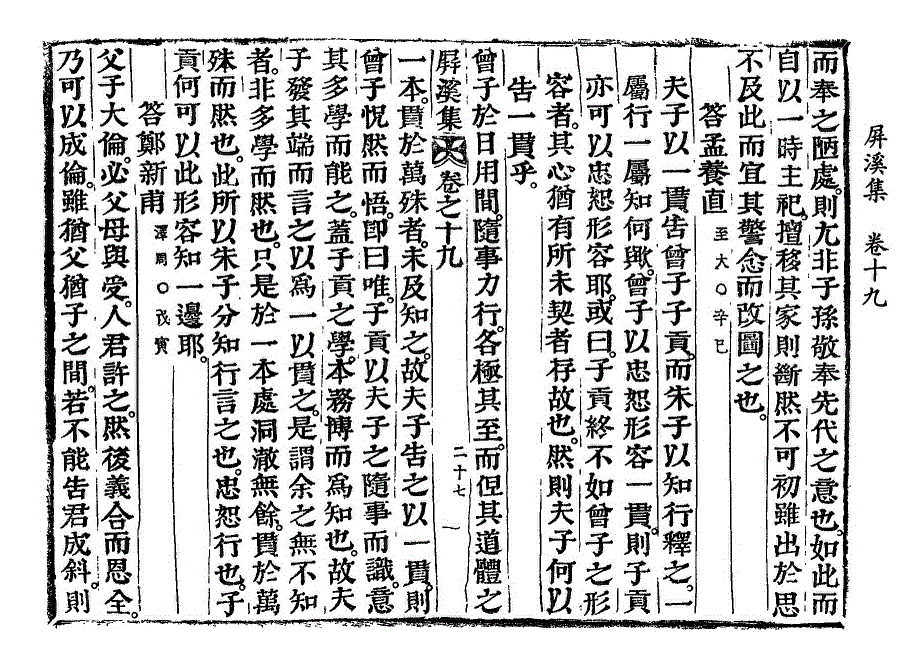 而奉之陋处。则尤非子孙敬奉先代之意也。如此而自以一时主祀。擅移其家则断然不可初虽出于思不及此而宜其警念而改图之也。
而奉之陋处。则尤非子孙敬奉先代之意也。如此而自以一时主祀。擅移其家则断然不可初虽出于思不及此而宜其警念而改图之也。答孟养直(至大○辛巳)
夫子以一贯告曾子子贡。而朱子以知行释之。一属行一属知何欤。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贯。则子贡亦可以忠恕形容耶。或曰。子贡终不如曾子之形容者。其心犹有所未契者存故也。然则夫子何以告一贯乎。
曾子于日用间。随事力行。各极其至。而但其道体之一本。贯于万殊者。未及知之。故夫子告之以一贯。则曾子恍然而悟。即曰唯。子贡以夫子之随事而识。意其多学而能之。盖子贡之学。本务博而为知也。故夫子发其端而言之以为一以贯之。是谓余之无不知者。非多学而然也。只是于一本处洞澈无馀。贯于万殊而然也。此所以朱子分知行言之也。忠恕行也。子贡何可以此形容知一边耶。
答郑新甫(泽周○戊寅)
父子大伦。必父母与受。人君许之。然后义合而恩全。乃可以成伦。虽犹父犹子之间。若不能告君成斜。则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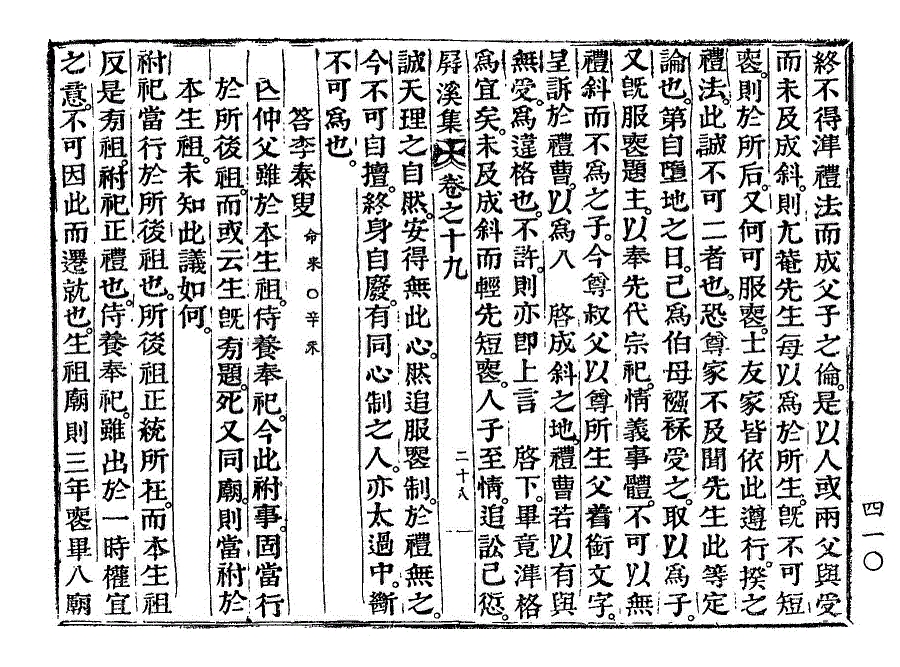 终不得准礼法而成父子之伦。是以人或两父与受而未及成斜。则尤庵先生每以为于所生。既不可短丧。则于所后。又何可服丧。士友家皆依此遵行。揆之礼法。此诚不可二者也。恐尊家不及闻先生此等定论也。第自堕地之日。已为伯母襁褓受之。取以为子。又既服丧题主。以奉先代宗祀。情义事体。不可以无礼斜而不为之子。今尊叔父以尊所生父着衔文字。呈诉于礼曹。以为入 启成斜之地。礼曹若以有与无受。为违格也。不许。则亦即上言 启下。毕竟准格为宜矣。未及成斜而轻先短丧。人子至情。追讼已愆。诚天理之自然。安得无此心。然追服丧制。于礼无之。今不可自擅。终身自废。有同心制之人。亦太过中。断不可为也。
终不得准礼法而成父子之伦。是以人或两父与受而未及成斜。则尤庵先生每以为于所生。既不可短丧。则于所后。又何可服丧。士友家皆依此遵行。揆之礼法。此诚不可二者也。恐尊家不及闻先生此等定论也。第自堕地之日。已为伯母襁褓受之。取以为子。又既服丧题主。以奉先代宗祀。情义事体。不可以无礼斜而不为之子。今尊叔父以尊所生父着衔文字。呈诉于礼曹。以为入 启成斜之地。礼曹若以有与无受。为违格也。不许。则亦即上言 启下。毕竟准格为宜矣。未及成斜而轻先短丧。人子至情。追讼已愆。诚天理之自然。安得无此心。然追服丧制。于礼无之。今不可自擅。终身自废。有同心制之人。亦太过中。断不可为也。答李泰叟(命来○辛未)
亡仲父虽于本生祖。侍养奉祀。今此祔事。固当行于所后祖。而或云生既旁题。死又同庙。则当祔于本生祖。未知此议如何。
祔祀当行于所后祖也。所后祖正统所在。而本生祖反是旁祖。祔祀正礼也。侍养奉祀。虽出于一时权宜之意。不可因此而迁就也。生祖庙则三年丧毕入庙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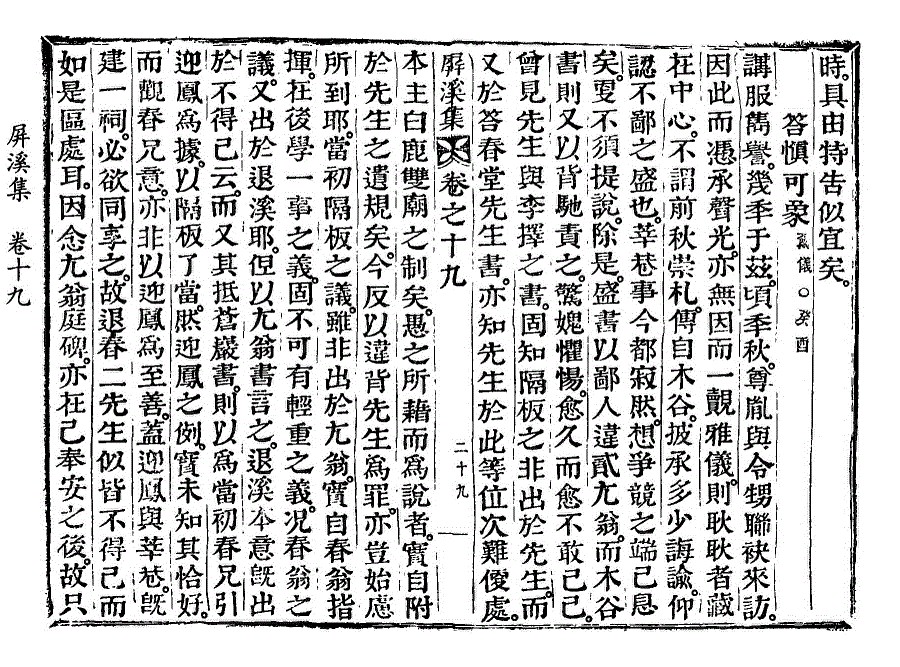 时。具由特告似宜矣。
时。具由特告似宜矣。答慎可象(尔仪○癸酉)
讲服隽誉。几年于兹。顷年秋。尊胤与令甥联袂来访。因此而凭承声光。亦无因而一觌雅仪。则耿耿者藏在中心。不谓前秋崇札。传自木谷。披承多少诲谕。仰认不鄙之盛也。莘巷事今都寂然。想争竞之端已息矣。更不须提说。除是。盛书以鄙人违贰尤翁。而木谷书则又以背驰责之。惊愧惧惕。愈久而愈不敢已已。曾见先生与李择之书。固知隔板之非出于先生。而又于答春堂先生书。亦知先生于此等位次难便处。本主白鹿双庙之制矣。愚之所藉而为说者。实自附于先生之遗规矣。今反以违背先生为罪。亦岂始虑所到耶。当初隔板之议。虽非出于尤翁。实自春翁指挥。在后学一事之义。固不可有轻重之义。况春翁之议。又出于退溪耶。但以尤翁书言之。退溪本意既出于不得已云。而又其抵苍岩书。则以为当初春兄引迎凤为据。以隔板了当。然迎凤之例。实未知其恰好。而观春兄意。亦非以迎凤为至善。盖迎凤与莘巷。既建一祠。必欲同享之。故退,春二先生似皆不得已而如是区处耳。因念尤翁庭碑。亦在已奉安之后。故只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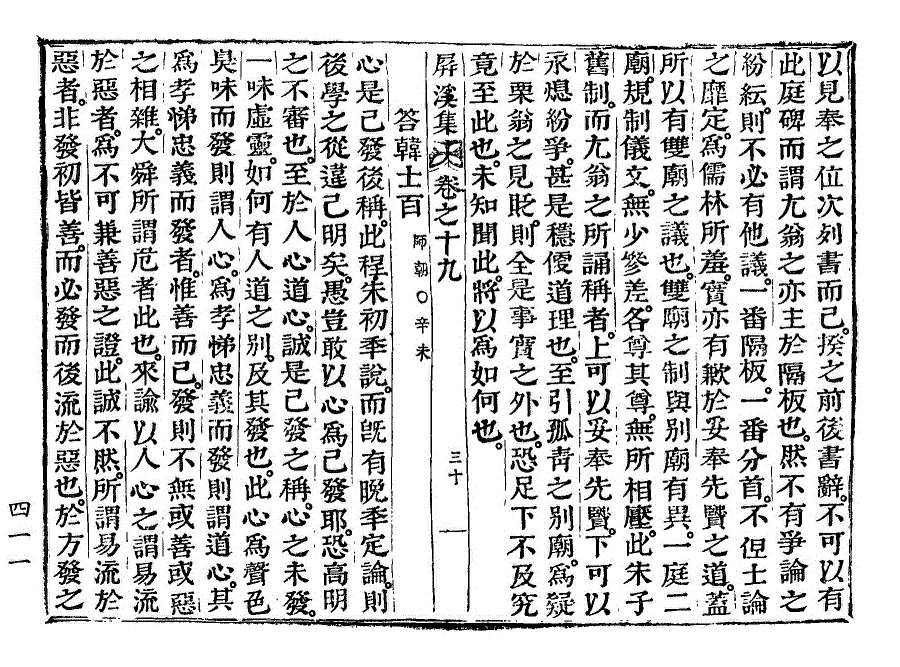 以见奉之位次列书而已。揆之前后书辞。不可以有此庭碑而谓尤翁之亦主于隔板也。然不有争论之纷纭。则不必有他议。一番隔板。一番分首。不但士论之靡定。为儒林所羞。实亦有歉于妥奉先贤之道。盖所以有双庙之议也。双庙之制与别庙有异。一庭二庙。规制仪文。无少参差。各尊其尊。无所相压。此朱子旧制。而尤翁之所诵称者。上可以妥奉先贤。下可以永熄纷争。甚是稳便道理也。至引孤青之别庙。为疑于栗翁之见贬。则全是事实之外也。恐足下不及究竟至此也。未知闻此。将以为如何也。
以见奉之位次列书而已。揆之前后书辞。不可以有此庭碑而谓尤翁之亦主于隔板也。然不有争论之纷纭。则不必有他议。一番隔板。一番分首。不但士论之靡定。为儒林所羞。实亦有歉于妥奉先贤之道。盖所以有双庙之议也。双庙之制与别庙有异。一庭二庙。规制仪文。无少参差。各尊其尊。无所相压。此朱子旧制。而尤翁之所诵称者。上可以妥奉先贤。下可以永熄纷争。甚是稳便道理也。至引孤青之别庙。为疑于栗翁之见贬。则全是事实之外也。恐足下不及究竟至此也。未知闻此。将以为如何也。答韩士百(师朝○辛未)
心是已发后称。此程,朱初年说。而既有晚年定论。则后学之从违已明矣。愚岂敢以心为已发耶。恐高明之不审也。至于人心道心。诚是已发之称。心之未发。一味虚灵。如何有人道之别。及其发也。此心为声色臭味而发则谓人心。为孝悌忠义而发则谓道心。其为孝悌忠义而发者。惟善而已。发则不无或善或恶之相杂。大舜所谓危者此也。来谕以人心之谓易流于恶者。为不可兼善恶之證。此诚不然。所谓易流于恶者。非发初皆善。而必发而后流于恶也。于方发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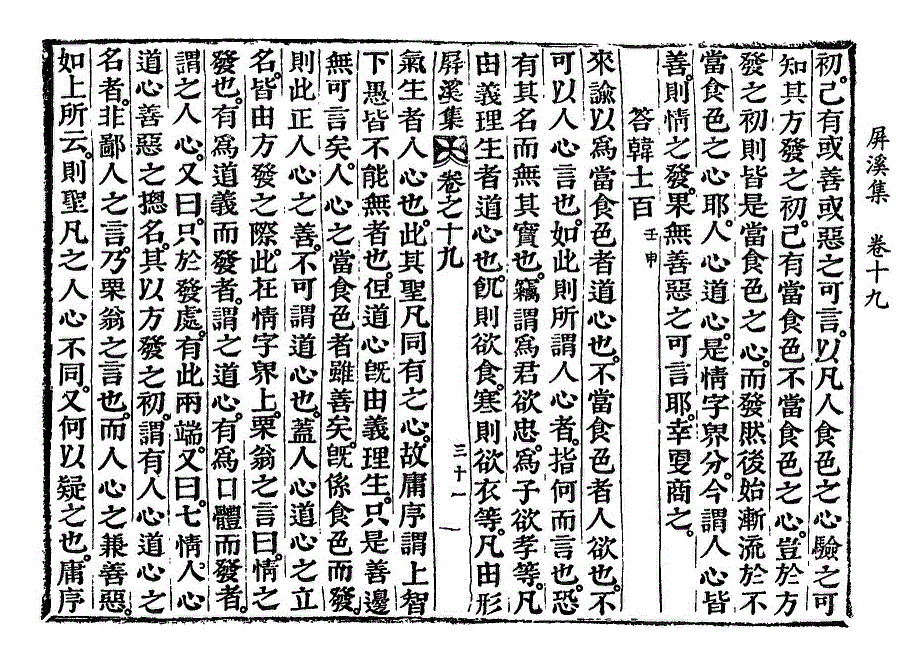 初。已有或善或恶之可言。以凡人食色之心验之可知其方发之初。已有当食色不当食色之心。岂于方发之初则皆是当食色之心。而发然后始渐流于不当食色之心耶。人心道心。是情字界分。今谓人心皆善。则情之发。果无善恶之可言耶。幸更商之。
初。已有或善或恶之可言。以凡人食色之心验之可知其方发之初。已有当食色不当食色之心。岂于方发之初则皆是当食色之心。而发然后始渐流于不当食色之心耶。人心道心。是情字界分。今谓人心皆善。则情之发。果无善恶之可言耶。幸更商之。答韩士百(壬申)
来谕以为当食色者道心也。不当食色者人欲也。不可以人心言也。如此则所谓人心者。指何而言也。恐有其名而无其实也。窃谓为君欲忠。为子欲孝等。凡由义理生者道心也。饥则欲食。寒则欲衣等。凡由形气生者人心也。此其圣凡同有之心。故庸序谓上智下愚皆不能无者也。但道心既由义理生。只是善边无可言矣。人心之当食色者虽善矣。既系食色而发。则此正人心之善。不可谓道心也。盖人心道心之立名。皆由方发之际。此在情字界上。栗翁之言曰。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谓之人心。又曰。只于发处。有此两端。又曰。七情。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其以方发之初。谓有人心道心之名者。非鄙人之言。乃栗翁之言也。而人心之兼善恶。如上所云。则圣凡之人心不同。又何以疑之也。庸序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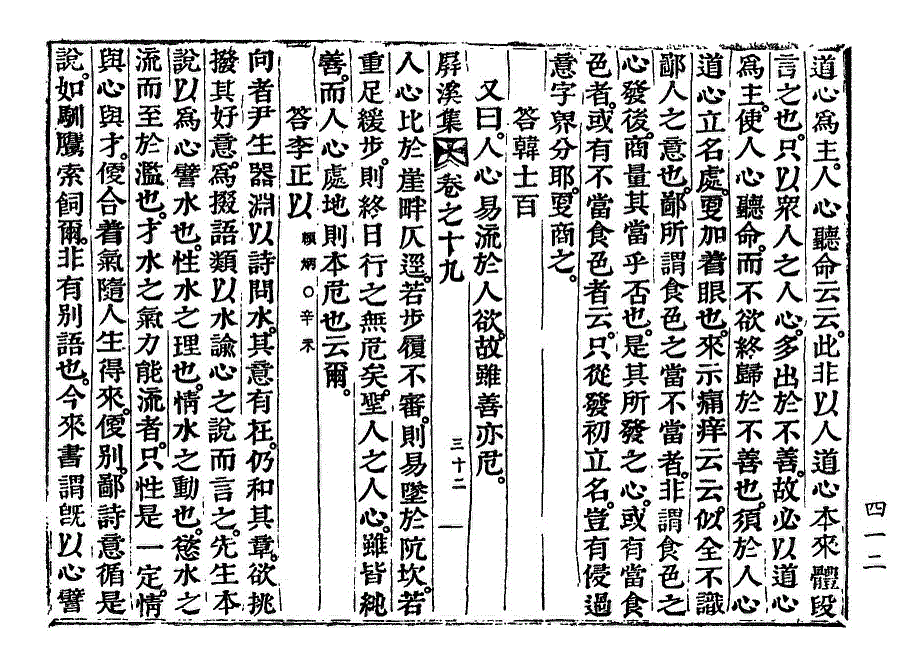 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云云。此非以人道心本来体段言之也。只以众人之人心。多出于不善。故必以道心为主。使人心听命。而不欲终归于不善也。须于人心道心立名处。更加着眼也。来示痛痒云云。似全不识鄙人之意也。鄙所谓食色之当不当者。非谓食色之心发后。商量其当乎否也。是其所发之心。或有当食色者。或有不当食色者云。只从发初立名。岂有侵过意字界分耶。更商之。
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云云。此非以人道心本来体段言之也。只以众人之人心。多出于不善。故必以道心为主。使人心听命。而不欲终归于不善也。须于人心道心立名处。更加着眼也。来示痛痒云云。似全不识鄙人之意也。鄙所谓食色之当不当者。非谓食色之心发后。商量其当乎否也。是其所发之心。或有当食色者。或有不当食色者云。只从发初立名。岂有侵过意字界分耶。更商之。答韩士百
又曰。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亦危。
人心比于崖畔仄径。若步履不审。则易坠于坑坎。若重足缓步。则终日行之无危矣。圣人之人心。虽皆纯善。而人心处地则本危也云尔。
答李正以(颐炳○辛未)
向者尹生器渊以诗问水。其意有在。仍和其章。欲挑拨其好意。为掇语类以水谕心之说而言之。先生本说以为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情水之动也。欲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水之气力能流者。只性是一定。情与心与才。便合着气随人生得来。便别。鄙诗意循是说。如驯鹰索饲尔。非有别语也。今来书谓既以心譬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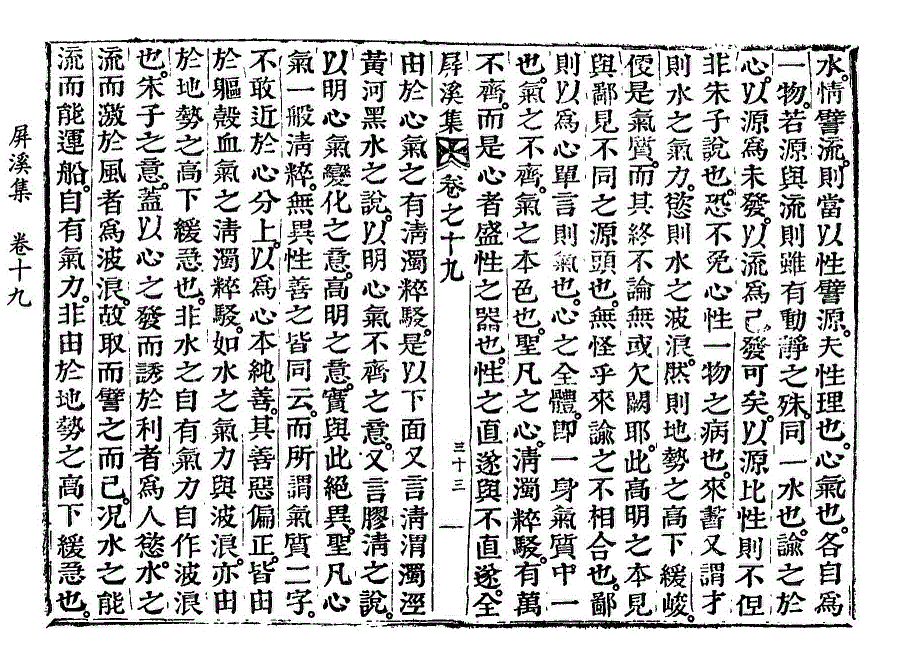 水。情譬流。则当以性譬源。夫性理也。心气也。各自为一物。若源与流则虽有动静之殊。同一水也。谕之于心。以源为未发。以流为已发可矣。以源比性则不但非朱子说也。恐不免心性一物之病也。来书又谓才则水之气力。欲则水之波浪。然则地势之高下缓峻。便是气质。而其终不论无或欠阙耶。此高明之本见与鄙见不同之源头也。无怪乎来谕之不相合也。鄙则以为心单言则气也。心之全体。即一身气质中一也。气之不齐。气之本色也。圣凡之心。清浊粹驳。有万不齐。而是心者盛性之器也。性之直遂与不直遂。全由于心气之有清浊粹驳。是以下面又言清渭浊泾黄河黑水之说。以明心气不齐之意。又言胶清之说。以明心气变化之意。高明之意。实与此绝异。圣凡心气一般清粹。无异性善之皆同云。而所谓气质二字。不敢近于心分上。以为心本纯善。其善恶偏正。皆由于躯壳血气之清浊粹驳。如水之气力与波浪。亦由于地势之高下缓急也。非水之自有气力自作波浪也。朱子之意。盖以心之发而诱于利者为人欲。水之流而激于风者为波浪。故取而譬之而已。况水之能流而能运船。自有气力。非由于地势之高下缓急也。
水。情譬流。则当以性譬源。夫性理也。心气也。各自为一物。若源与流则虽有动静之殊。同一水也。谕之于心。以源为未发。以流为已发可矣。以源比性则不但非朱子说也。恐不免心性一物之病也。来书又谓才则水之气力。欲则水之波浪。然则地势之高下缓峻。便是气质。而其终不论无或欠阙耶。此高明之本见与鄙见不同之源头也。无怪乎来谕之不相合也。鄙则以为心单言则气也。心之全体。即一身气质中一也。气之不齐。气之本色也。圣凡之心。清浊粹驳。有万不齐。而是心者盛性之器也。性之直遂与不直遂。全由于心气之有清浊粹驳。是以下面又言清渭浊泾黄河黑水之说。以明心气不齐之意。又言胶清之说。以明心气变化之意。高明之意。实与此绝异。圣凡心气一般清粹。无异性善之皆同云。而所谓气质二字。不敢近于心分上。以为心本纯善。其善恶偏正。皆由于躯壳血气之清浊粹驳。如水之气力与波浪。亦由于地势之高下缓急也。非水之自有气力自作波浪也。朱子之意。盖以心之发而诱于利者为人欲。水之流而激于风者为波浪。故取而譬之而已。况水之能流而能运船。自有气力。非由于地势之高下缓急也。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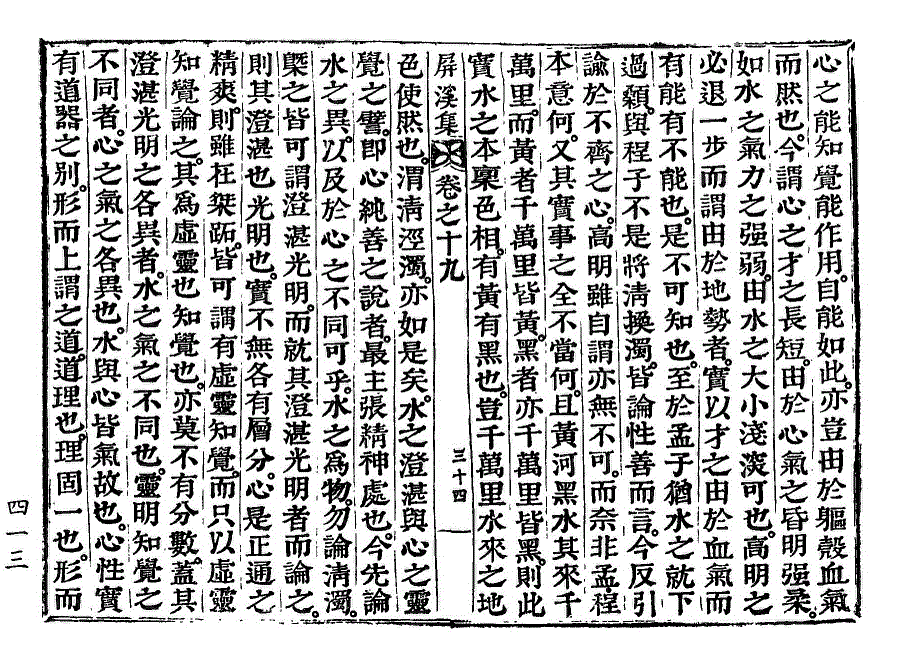 心之能知觉能作用。自能如此。亦岂由于躯壳血气而然也。今谓心之才之长短。由于心气之昏明强柔。如水之气力之强弱。由水之大小浅深可也。高明之必退一步而谓由于地势者。实以才之由于血气而有能有不能也。是不可知也。至于孟子犹水之就下过颡。与程子不是将清换浊。皆论性善而言。今反引谕于不齐之心。高明虽自谓亦无不可。而奈非孟,程本意何。又其实事之全不当何。且黄河黑水其来千万里。而黄者千万里皆黄。黑者亦千万里皆黑。则此实水之本禀色相。有黄有黑也。岂千万里水来之地色使然也。渭清泾浊。亦如是矣。水之澄湛与心之灵觉之譬。即心纯善之说者。最主张精神处也。今先论水之异。以及于心之不同可乎。水之为物。勿论清浊。槩之皆可谓澄湛光明。而就其澄湛光明者而论之。则其澄湛也光明也。实不无各有层分。心是正通之精爽。则虽在桀蹠。皆可谓有虚灵知觉。而只以虚灵知觉论之。其为虚灵也知觉也。亦莫不有分数。盖其澄湛光明之各异者。水之气之不同也。灵明知觉之不同者。心之气之各异也。水与心皆气故也。心性实有道器之别。形而上谓之道。道理也。理固一也。形而
心之能知觉能作用。自能如此。亦岂由于躯壳血气而然也。今谓心之才之长短。由于心气之昏明强柔。如水之气力之强弱。由水之大小浅深可也。高明之必退一步而谓由于地势者。实以才之由于血气而有能有不能也。是不可知也。至于孟子犹水之就下过颡。与程子不是将清换浊。皆论性善而言。今反引谕于不齐之心。高明虽自谓亦无不可。而奈非孟,程本意何。又其实事之全不当何。且黄河黑水其来千万里。而黄者千万里皆黄。黑者亦千万里皆黑。则此实水之本禀色相。有黄有黑也。岂千万里水来之地色使然也。渭清泾浊。亦如是矣。水之澄湛与心之灵觉之譬。即心纯善之说者。最主张精神处也。今先论水之异。以及于心之不同可乎。水之为物。勿论清浊。槩之皆可谓澄湛光明。而就其澄湛光明者而论之。则其澄湛也光明也。实不无各有层分。心是正通之精爽。则虽在桀蹠。皆可谓有虚灵知觉。而只以虚灵知觉论之。其为虚灵也知觉也。亦莫不有分数。盖其澄湛光明之各异者。水之气之不同也。灵明知觉之不同者。心之气之各异也。水与心皆气故也。心性实有道器之别。形而上谓之道。道理也。理固一也。形而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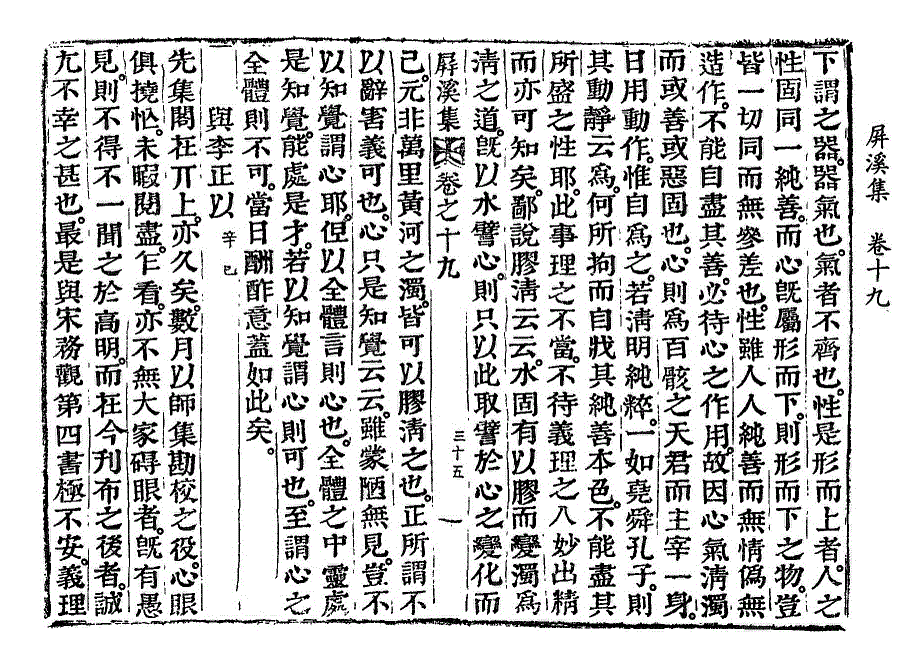 下谓之器。器气也。气者不齐也。性是形而上者。人之性固同一纯善。而心既属形而下。则形而下之物。岂皆一切同而无参差也。性虽人人纯善而无情伪无造作。不能自尽其善。必待心之作用。故因心气清浊而或善或恶固也。心则为百骸之天君而主宰一身。日用动作。惟自为之。若清明纯粹。一如尧舜孔子。则其动静云为。何所拘而自戕其纯善本色。不能尽其所盛之性耶。此事理之不当。不待义理之入妙出精而亦可知矣。鄙说胶清云云。水固有以胶而变浊为清之道。既以水譬心。则只以此取譬于心之变化而已。元非万里黄河之浊。皆可以胶清之也。正所谓不以辞害义可也。心只是知觉云云。虽蒙陋无见。岂不以知觉谓心耶。但以全体言则心也。全体之中灵处是知觉。能处是才。若以知觉谓心则可也。至谓心之全体则不可。当日酬酢意盖如此矣。
下谓之器。器气也。气者不齐也。性是形而上者。人之性固同一纯善。而心既属形而下。则形而下之物。岂皆一切同而无参差也。性虽人人纯善而无情伪无造作。不能自尽其善。必待心之作用。故因心气清浊而或善或恶固也。心则为百骸之天君而主宰一身。日用动作。惟自为之。若清明纯粹。一如尧舜孔子。则其动静云为。何所拘而自戕其纯善本色。不能尽其所盛之性耶。此事理之不当。不待义理之入妙出精而亦可知矣。鄙说胶清云云。水固有以胶而变浊为清之道。既以水譬心。则只以此取譬于心之变化而已。元非万里黄河之浊。皆可以胶清之也。正所谓不以辞害义可也。心只是知觉云云。虽蒙陋无见。岂不以知觉谓心耶。但以全体言则心也。全体之中灵处是知觉。能处是才。若以知觉谓心则可也。至谓心之全体则不可。当日酬酢意盖如此矣。与李正以(辛巳)
先集阁在丌上。亦久矣。数月以师集勘校之役。心眼俱挠忙。未暇阅尽。乍看。亦不无大家碍眼者。既有愚见。则不得不一闻之于高明。而在今刊布之后者。诚尤不幸之甚也。最是与宋务观第四书极不安。义理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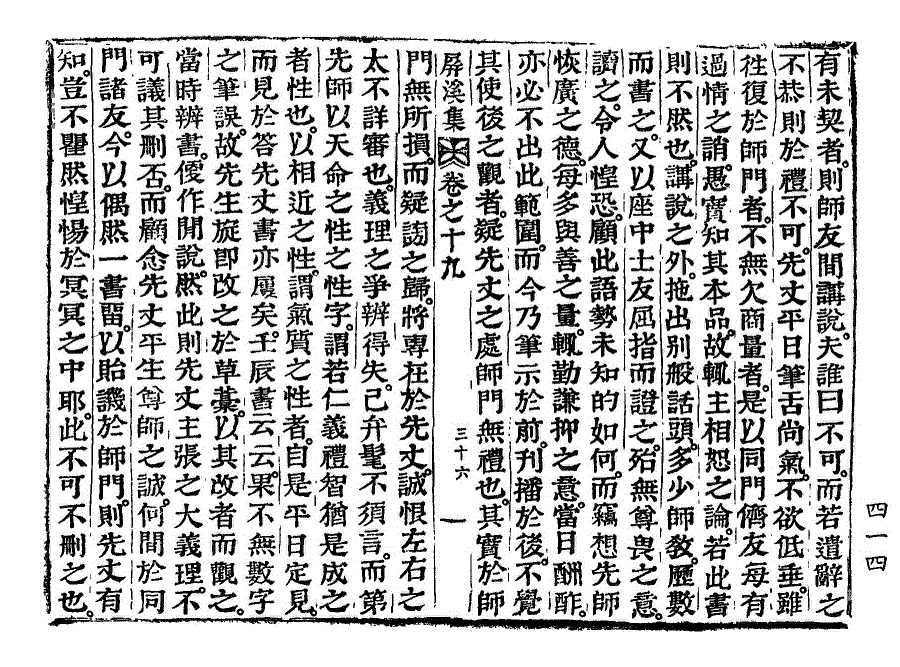 有未契者。则师友间讲说。夫谁曰不可。而若遣辞之不恭则于礼不可。先丈平日笔舌尚气。不欲低垂。虽往复于师门者。不无欠商量者。是以同门侪友每有过情之诮。愚实知其本品。故辄主相恕之论。若此书则不然也。讲说之外。拖出别般话头。多少师教。历数而书之。又以座中士友屈指而證之。殆无尊畏之意。读之。令人惶恐。顾此语势未知的如何。而窃想先师恢广之德。每多与善之量。辄勤谦抑之意。当日酬酢。亦必不出此范围。而今乃笔示于前。刊播于后。不觉其使后之观者。疑先丈之处师门无礼也。其实于师门无所损。而疑谤之归。将专在于先丈。诚恨左右之太不详审也。义理之争辨得失。已弁髦不须言。而第先师以天命之性之性字。谓若仁义礼智犹是成之者性也。以相近之性。谓气质之性者。自是平日定见。而见于答先丈书亦屡矣。壬辰书云云。果不无数字之笔误。故先生旋即改之于草藁。以其改者而观之。当时辨书。便作閒说。然此则先丈主张之大义理。不可议其删否。而顾念先丈平生尊师之诚。何间于同门诸友。今以偶然一书留。以贻讥于师门。则先丈有知。岂不瞿然惶惕于冥冥之中耶。此不可不删之也。
有未契者。则师友间讲说。夫谁曰不可。而若遣辞之不恭则于礼不可。先丈平日笔舌尚气。不欲低垂。虽往复于师门者。不无欠商量者。是以同门侪友每有过情之诮。愚实知其本品。故辄主相恕之论。若此书则不然也。讲说之外。拖出别般话头。多少师教。历数而书之。又以座中士友屈指而證之。殆无尊畏之意。读之。令人惶恐。顾此语势未知的如何。而窃想先师恢广之德。每多与善之量。辄勤谦抑之意。当日酬酢。亦必不出此范围。而今乃笔示于前。刊播于后。不觉其使后之观者。疑先丈之处师门无礼也。其实于师门无所损。而疑谤之归。将专在于先丈。诚恨左右之太不详审也。义理之争辨得失。已弁髦不须言。而第先师以天命之性之性字。谓若仁义礼智犹是成之者性也。以相近之性。谓气质之性者。自是平日定见。而见于答先丈书亦屡矣。壬辰书云云。果不无数字之笔误。故先生旋即改之于草藁。以其改者而观之。当时辨书。便作閒说。然此则先丈主张之大义理。不可议其删否。而顾念先丈平生尊师之诚。何间于同门诸友。今以偶然一书留。以贻讥于师门。则先丈有知。岂不瞿然惶惕于冥冥之中耶。此不可不删之也。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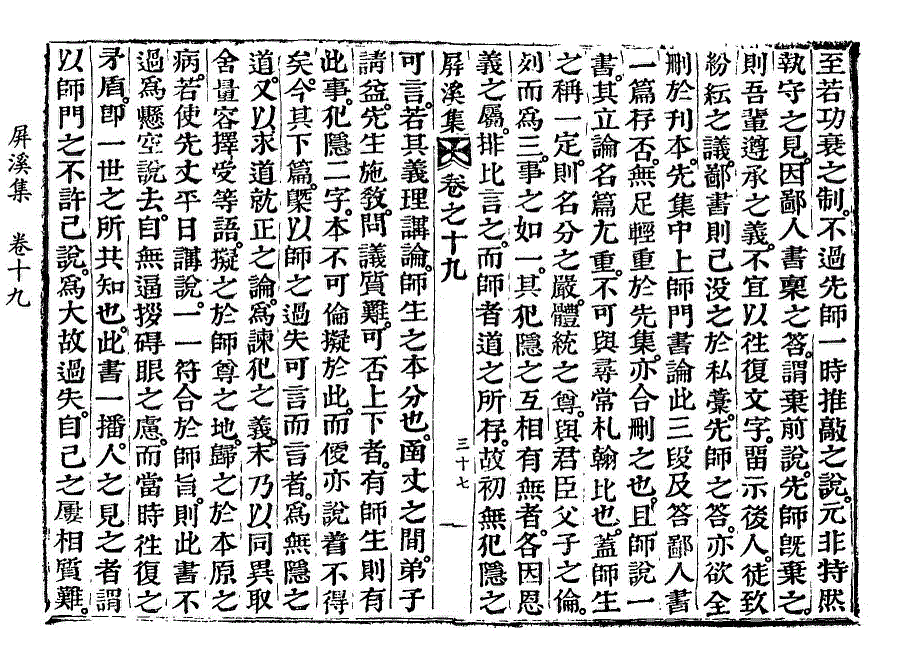 至若功衰之制。不过先师一时推敲之说。元非特然执守之见。因鄙人书禀之答。谓弃前说。先师既弃之。则吾辈遵承之义。不宜以往复文字。留示后人。徒致纷纭之议。鄙书则已没之于私藁。先师之答。亦欲全删于刊本。先集中上师门书论此三段及答鄙人书一篇存否。无足轻重于先集。亦合删之也。且师说一书。其立论名篇尤重。不可与寻常札翰比也。盖师生之称一定。则名分之严。体统之尊。与君臣父子之伦。列而为三。事之如一。其犯隐之互相有无者。各因恩义之属。排比言之。而师者道之所存。故初无犯隐之可言。若其义理讲论。师生之本分也。函丈之间。弟子请益。先生施教。问议质难。可否上下者。有师生则有此事。犯隐二字。本不可伦拟于此。而便亦说着不得矣。今其下篇。槩以师之过失可言而言者。为无隐之道。又以求道就正之论。为谏犯之义。末乃以同异取舍量容择受等语。拟之于师尊之地。归之于本原之病。若使先丈平日讲说。一一符合于师旨。则此书不过为悬空说去。自无逼拶碍眼之虑。而当时往复之矛盾。即一世之所共知也。此书一播。人之见之者谓以师门之不许己说。为大故过失。自己之屡相质难。
至若功衰之制。不过先师一时推敲之说。元非特然执守之见。因鄙人书禀之答。谓弃前说。先师既弃之。则吾辈遵承之义。不宜以往复文字。留示后人。徒致纷纭之议。鄙书则已没之于私藁。先师之答。亦欲全删于刊本。先集中上师门书论此三段及答鄙人书一篇存否。无足轻重于先集。亦合删之也。且师说一书。其立论名篇尤重。不可与寻常札翰比也。盖师生之称一定。则名分之严。体统之尊。与君臣父子之伦。列而为三。事之如一。其犯隐之互相有无者。各因恩义之属。排比言之。而师者道之所存。故初无犯隐之可言。若其义理讲论。师生之本分也。函丈之间。弟子请益。先生施教。问议质难。可否上下者。有师生则有此事。犯隐二字。本不可伦拟于此。而便亦说着不得矣。今其下篇。槩以师之过失可言而言者。为无隐之道。又以求道就正之论。为谏犯之义。末乃以同异取舍量容择受等语。拟之于师尊之地。归之于本原之病。若使先丈平日讲说。一一符合于师旨。则此书不过为悬空说去。自无逼拶碍眼之虑。而当时往复之矛盾。即一世之所共知也。此书一播。人之见之者谓以师门之不许己说。为大故过失。自己之屡相质难。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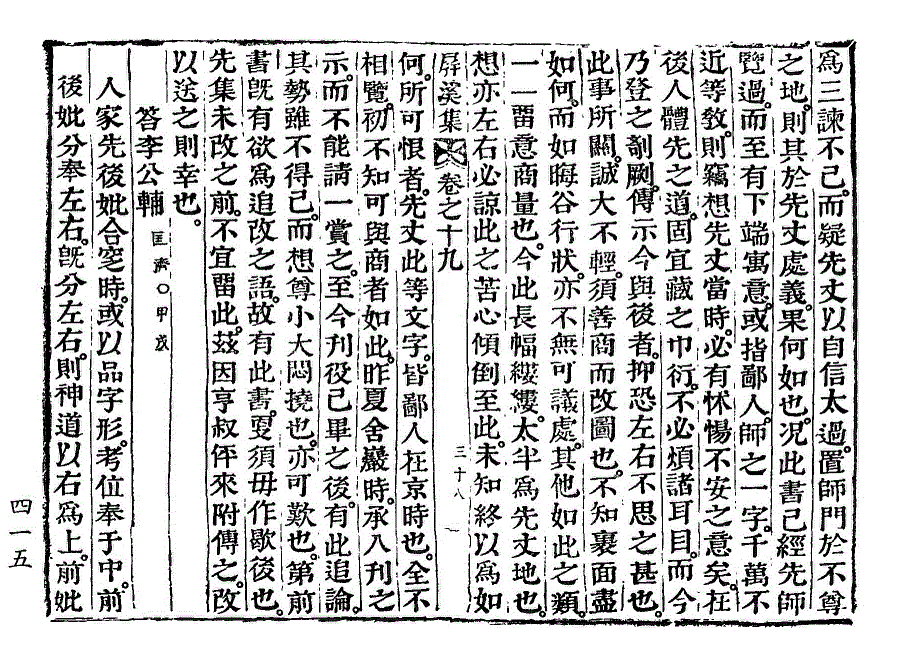 为三谏不已。而疑先丈以自信太过。置师门于不尊之地。则其于先丈处义。果何如也。况此书已经先师览过。而至有下端寓意。或指鄙人。师之一字。千万不近等教。则窃想先丈当时。必有怵惕不安之意矣。在后人体先之道。固宜藏之巾衍。不必烦诸耳目。而今乃登之剞劂。传示今与后者。抑恐左右不思之甚也。此事所关。诚大不轻。须善商而改图也。不知裹面尽如何。而如晦谷行状。亦不无可议处。其他如此之类。一一留意商量也。今此长幅缕缕。太半为先丈地也。想亦左右必谅此之苦心倾倒至此。未知终以为如何。所可恨者。先丈此等文字。皆鄙人在京时也。全不相览。初不知可与商者如此。昨夏舍岩时。承入刊之示。而不能请一赏之。至今刊役已毕之后。有此追论。其势虽不得已。而想尊小大闷挠也。亦可叹也。第前书既有欲为追改之语。故有此书。更须毋作歇后也。先集未改之前。不宜留此。兹因亨叔伻来附传之。改以送之则幸也。
为三谏不已。而疑先丈以自信太过。置师门于不尊之地。则其于先丈处义。果何如也。况此书已经先师览过。而至有下端寓意。或指鄙人。师之一字。千万不近等教。则窃想先丈当时。必有怵惕不安之意矣。在后人体先之道。固宜藏之巾衍。不必烦诸耳目。而今乃登之剞劂。传示今与后者。抑恐左右不思之甚也。此事所关。诚大不轻。须善商而改图也。不知裹面尽如何。而如晦谷行状。亦不无可议处。其他如此之类。一一留意商量也。今此长幅缕缕。太半为先丈地也。想亦左右必谅此之苦心倾倒至此。未知终以为如何。所可恨者。先丈此等文字。皆鄙人在京时也。全不相览。初不知可与商者如此。昨夏舍岩时。承入刊之示。而不能请一赏之。至今刊役已毕之后。有此追论。其势虽不得已。而想尊小大闷挠也。亦可叹也。第前书既有欲为追改之语。故有此书。更须毋作歇后也。先集未改之前。不宜留此。兹因亨叔伻来附传之。改以送之则幸也。答李公辅(匡济○甲戌)
人家先后妣合窆时。或以品字形。考位奉于中。前后妣分奉左右。既分左右。则神道以右为上。前妣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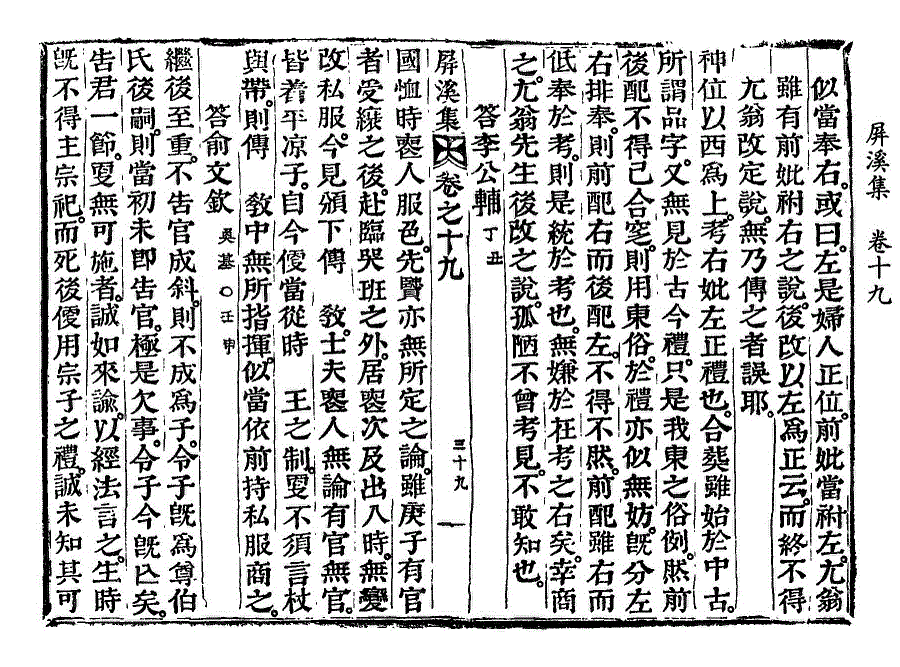 似当奉右。或曰。左是妇人正位。前妣当祔左。尤翁虽有前妣祔右之说。后改以左为正云。而终不得尤翁改定说。无乃传之者误耶。
似当奉右。或曰。左是妇人正位。前妣当祔左。尤翁虽有前妣祔右之说。后改以左为正云。而终不得尤翁改定说。无乃传之者误耶。神位以西为上。考右妣左正礼也。合葬虽始于中古。所谓品字。又无见于古今礼。只是我东之俗例。然前后配不得已合窆。则用东俗。于礼亦似无妨。既分左右排奉。则前配右而后配左。不得不然。前配虽右而低奉于考。则是统于考也。无嫌于在考之右矣。幸商之。尤翁先生后改之说。孤陋不曾考见。不敢知也。
答李公辅(丁丑)
国恤时丧人服色。先贤亦无所定之论。虽庚子有官者受缞之后。赴临哭班之外。居丧次及出入时。无变改私服。今见颁下传 教。士夫丧人无论有官无官。皆着平凉子。自今便当从时 王之制。更不须言杖与带。则传 教中无所指挥。似当依前持私服商之。
答俞文钦(奂基○壬申)
继后至重。不告官成斜。则不成为子。令子既为尊伯氏后嗣。则当初未即告官。极是欠事。令子今既亡矣。告君一节。更无可施者。诚如来谕。以经法言之。生时既不得主宗祀。而死后便用宗子之礼。诚未知其可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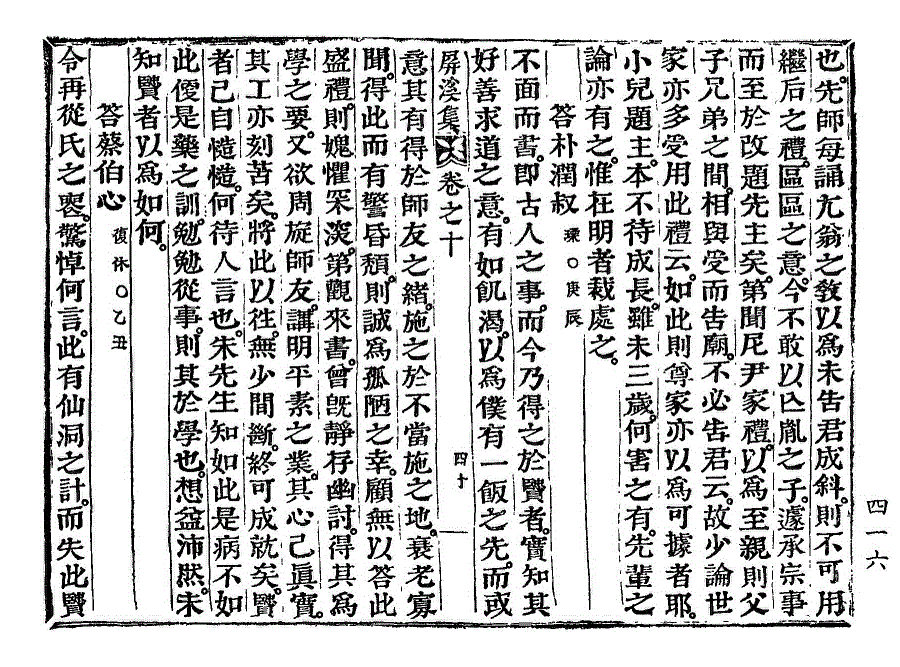 也。先师每诵尤翁之教以为未告君成斜。则不可用继后之礼。区区之意。今不敢以亡胤之子。遽承宗事而至于改题先主矣。第闻尼尹家礼。以为至亲则父子兄弟之间。相与受而告庙。不必告君云。故少论世家亦多受用此礼云。如此则尊家亦以为可据者耶。小儿题主。本不待成长。虽未三岁。何害之有。先辈之论亦有之。惟在明者裁处之。
也。先师每诵尤翁之教以为未告君成斜。则不可用继后之礼。区区之意。今不敢以亡胤之子。遽承宗事而至于改题先主矣。第闻尼尹家礼。以为至亲则父子兄弟之间。相与受而告庙。不必告君云。故少论世家亦多受用此礼云。如此则尊家亦以为可据者耶。小儿题主。本不待成长。虽未三岁。何害之有。先辈之论亦有之。惟在明者裁处之。答朴润叔(瑮○庚辰)
不面而书。即古人之事。而今乃得之于贤者。实知其好善求道之意。有如饥渴。以为仆有一饭之先。而或意其有得于师友之绪。施之于不当施之地。衰老寡闻。得此而有警昏颓。则诚为孤陋之幸。顾无以答此盛礼。则愧惧深深。第观来书。曾既静存幽讨。得其为学之要。又欲周旋师友。讲明平素之业。其心已真实。其工亦刻苦矣。将此以往。无少间断。终可成就矣。贤者已自慥慥。何待人言也。朱先生知如此是病不如此便是药之训。勉勉从事。则其于学也。想益沛然。未知贤者以为如何。
答蔡伯心(复休○乙丑)
令再从氏之丧。惊悼何言。此有仙洞之计。而失此贤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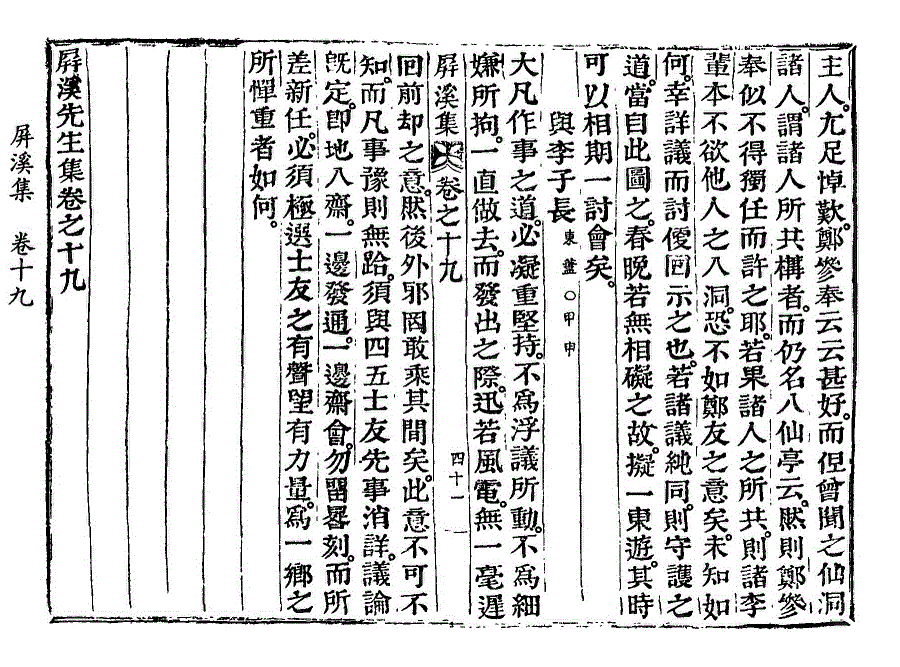 主人。尤足悼叹。郑参奉云云甚好。而但曾闻之仙洞诸人。谓诸人所共构者。而仍名八仙亭云。然则郑参奉似不得独任而许之耶。若果诸人之所共。则诸李辈本不欲他人之入洞。恐不如郑友之意矣。未知如何。幸详议而讨便回示之也。若诸议纯同。则守护之道。当自此图之。春晚若无相碍之故。拟一东游。其时可以相期一讨会矣。
主人。尤足悼叹。郑参奉云云甚好。而但曾闻之仙洞诸人。谓诸人所共构者。而仍名八仙亭云。然则郑参奉似不得独任而许之耶。若果诸人之所共。则诸李辈本不欲他人之入洞。恐不如郑友之意矣。未知如何。幸详议而讨便回示之也。若诸议纯同。则守护之道。当自此图之。春晚若无相碍之故。拟一东游。其时可以相期一讨会矣。与李子长(东荩○甲申)
大凡作事之道。必凝重坚持。不为浮议所动。不为细嫌所拘。一直做去。而发出之际。迅若风电。无一毫迟回前却之意。然后外邪罔敢乘其间矣。此意不可不知。而凡事豫则无跲。须与四五士友先事消详。议论既定。即地入斋。一边发通。一边斋会。勿留晷刻。而所差新任。必须极选士友之有声望有力量。为一乡之所惮重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