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书
答李敬工(颐正○辛酉)
嫡庶之分。实同宗支之别。支子不得祭其祢。而必宗孙主其祀。则今当祧主之迁。嫡曾玄之亲不尽者必奉其祭。虽有庶子庶孙。不可议矣。果使嫡庶无别。一例以行年迁次。则人有嫡庶子而庶长于嫡。其以庶子奉祀耶。由此言之。无论行列高下年岁多少。嫡先于庶者明矣。下询云云嫡庶之争。似无难处之端焉。
书
答李敬工(颐正○辛酉)
嫡庶之分。实同宗支之别。支子不得祭其祢。而必宗孙主其祀。则今当祧主之迁。嫡曾玄之亲不尽者必奉其祭。虽有庶子庶孙。不可议矣。果使嫡庶无别。一例以行年迁次。则人有嫡庶子而庶长于嫡。其以庶子奉祀耶。由此言之。无论行列高下年岁多少。嫡先于庶者明矣。下询云云嫡庶之争。似无难处之端焉。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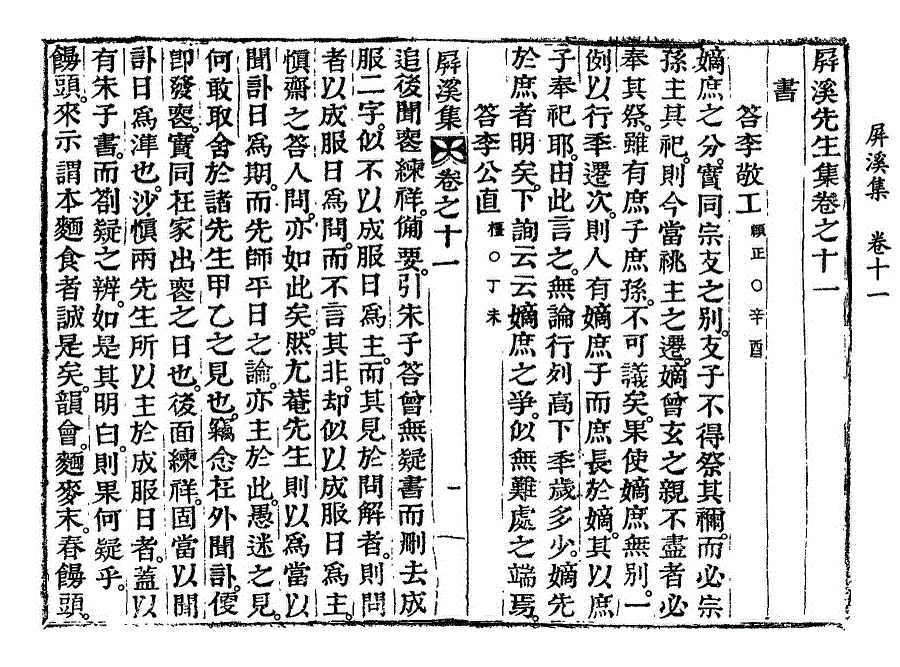 答李公直(橿○丁未)
答李公直(橿○丁未)追后闻丧练祥。备要。引朱子答曾无疑书而删去成服二字。似不以成服日为主。而其见于问解者。则问者以成服日为问。而不言其非。却似以成服日为主。慎斋之答人问。亦如此矣。然尤庵先生则以为当以闻讣日为期。而先师平日之论。亦主于此。愚迷之见。何敢取舍于诸先生甲乙之见也。窃念在外闻讣。便即发丧。实同在家出丧之日也。后面练祥。固当以闻讣日为准也。沙,慎两先生所以主于成服日者。盖以有朱子书。而劄疑之辨。如是其明白。则果何疑乎。
馒头。来示谓本面食者诚是矣。韵会。面麦末。春馒头。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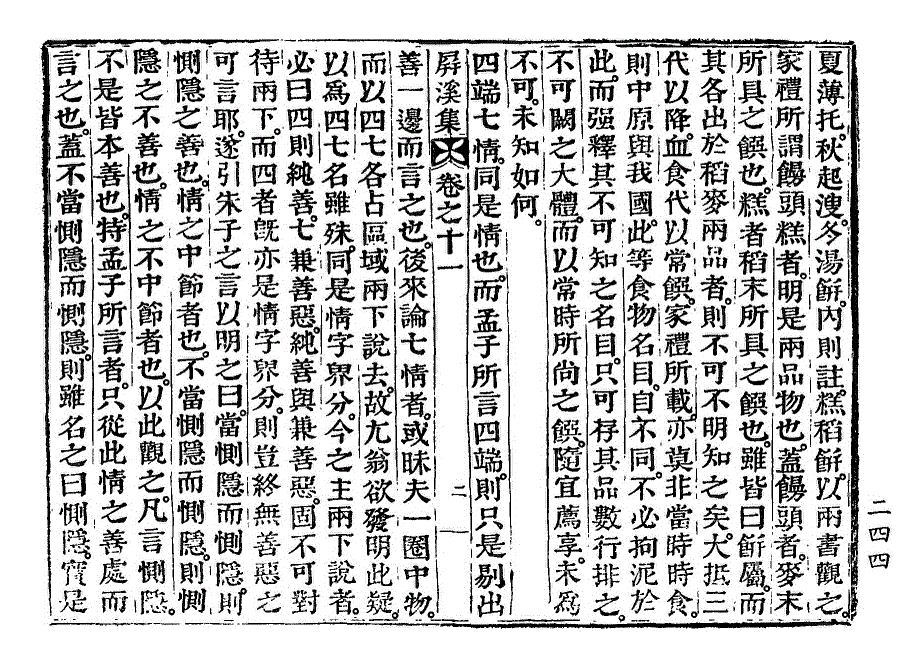 夏薄托。秋起溲。冬汤饼。内则注。糕稻饼。以两书观之。家礼所谓馒头糕者。明是两品物也。盖馒头者。麦末所具之馔也。糕者稻末所具之馔也。虽皆曰饼属。而其各出于稻麦两品者。则不可不明知之矣。大抵三代以降。血食代以常馔。家礼所载。亦莫非当时时食。则中原与我国。此等食物名目。自不同。不必拘泥于此。而强释其不可知之名目。只可存其品数行排之。不可阙之大体。而以常时所尚之馔。随宜荐享。未为不可。未知如何。
夏薄托。秋起溲。冬汤饼。内则注。糕稻饼。以两书观之。家礼所谓馒头糕者。明是两品物也。盖馒头者。麦末所具之馔也。糕者稻末所具之馔也。虽皆曰饼属。而其各出于稻麦两品者。则不可不明知之矣。大抵三代以降。血食代以常馔。家礼所载。亦莫非当时时食。则中原与我国。此等食物名目。自不同。不必拘泥于此。而强释其不可知之名目。只可存其品数行排之。不可阙之大体。而以常时所尚之馔。随宜荐享。未为不可。未知如何。四端七情。同是情也。而孟子所言四端。则只是剔出善一边而言之也。后来论七情者。或昧夫一圈中物。而以四七各占区域两下说去。故尤翁欲发明此疑。以为四七名虽殊。同是情字界分。今之主两下说者。必曰四则纯善。七兼善恶。纯善与兼善恶。固不可对待两下。而四者既亦是情字界分。则岂终无善恶之可言耶。遂引朱子之言以明之曰。当恻隐而恻隐。则恻隐之善也。情之中节者也。不当恻隐而恻隐。则恻隐之不善也。情之不中节者也。以此观之。凡言恻隐。不是皆本善也。特孟子所言者。只从此情之善处而言之也。盖不当恻隐而恻隐。则虽名之曰恻隐。实是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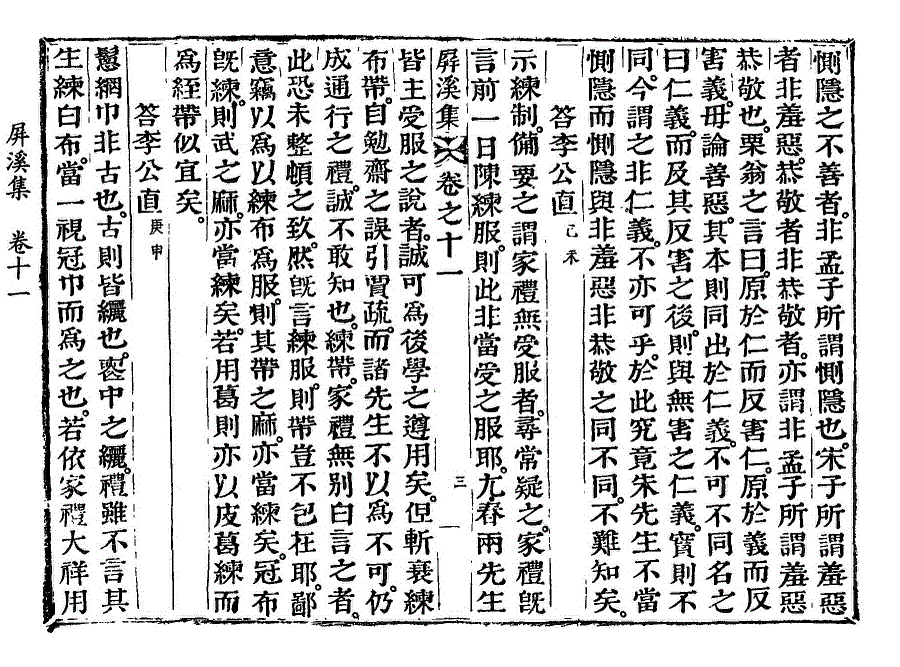 恻隐之不善者。非孟子所谓恻隐也。朱子所谓羞恶者非羞恶。恭敬者非恭敬者。亦谓非孟子所谓羞恶恭敬也。栗翁之言曰。原于仁而反害仁。原于义而反害义。毋论善恶。其本则同出于仁义。不可不同名之曰仁义。而及其反害之后。则与无害之仁义。实则不同。今谓之非仁义。不亦可乎。于此究竟朱先生不当恻隐而恻隐与非羞恶非恭敬之同不同。不难知矣。
恻隐之不善者。非孟子所谓恻隐也。朱子所谓羞恶者非羞恶。恭敬者非恭敬者。亦谓非孟子所谓羞恶恭敬也。栗翁之言曰。原于仁而反害仁。原于义而反害义。毋论善恶。其本则同出于仁义。不可不同名之曰仁义。而及其反害之后。则与无害之仁义。实则不同。今谓之非仁义。不亦可乎。于此究竟朱先生不当恻隐而恻隐与非羞恶非恭敬之同不同。不难知矣。答李公直(己未)
示练制。备要之谓家礼无受服者。寻常疑之。家礼既言前一日陈练服。则此非当受之服耶。尤,春两先生皆主受服之说者。诚可为后学之遵用矣。但斩衰练布带。自勉斋之误引贾疏。而诸先生不以为不可。仍成通行之礼。诚不敢知也。练带。家礼无别白言之者。此恐未整顿之致。然既言练服。则带岂不包在耶。鄙意窃以为以练布为服。则其带之麻。亦当练矣。冠布既练。则武之麻。亦当练矣。若用葛则亦以皮葛练而为绖带似宜矣。
答李公直(庚申)
𩮰网巾非古也。古则皆纚也。丧中之纚。礼虽不言其生练白布。当一视冠巾而为之也。若依家礼大祥用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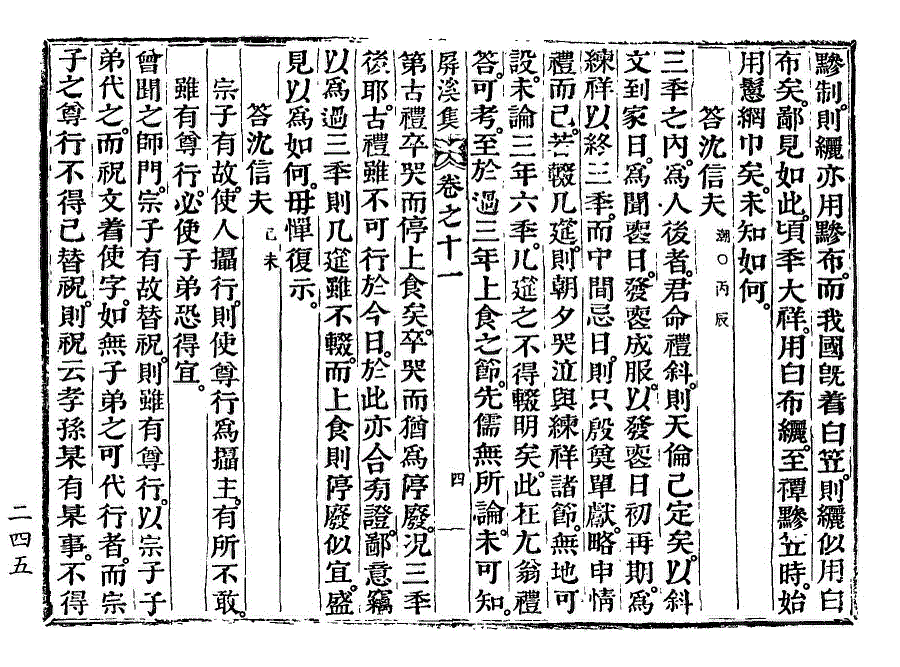 黪制。则纚亦用黪布。而我国既着白笠。则纚似用白布矣。鄙见如此。顷年大祥。用白布纚。至禫黪笠时。始用𩮰网巾矣。未知如何。
黪制。则纚亦用黪布。而我国既着白笠。则纚似用白布矣。鄙见如此。顷年大祥。用白布纚。至禫黪笠时。始用𩮰网巾矣。未知如何。答沈信夫(潮○丙辰)
三年之内。为人后者。君命礼斜。则天伦已定矣。以斜文到家日。为闻丧日。发丧成服。以发丧日初再期。为练祥以终三年。而中间忌日。则只殷奠单献。略申情礼而已。若辍几筵。则朝夕哭泣与练祥诸节。无地可设。未论三年六年。几筵之不得辍明矣。此在尤翁礼答。可考。至于过三年上食之节。先儒无所论。未可知。第古礼卒哭而停上食矣。卒哭而犹为停废。况三年后耶。古礼虽不可行于今日。于此亦合旁證。鄙意窃以为过三年则几筵虽不辍。而上食则停废似宜。盛见以为如何。毋惮复示。
答沈信夫(己未)
宗子有故。使人摄行。则使尊行为摄主。有所不敢。虽有尊行。必使子弟恐得宜。
曾闻之师门。宗子有故替祝。则虽有尊行。以宗子子弟代之。而祝文着使字。如无子弟之可代行者。而宗子之尊行不得已替祝。则祝云孝孙某有某事。不得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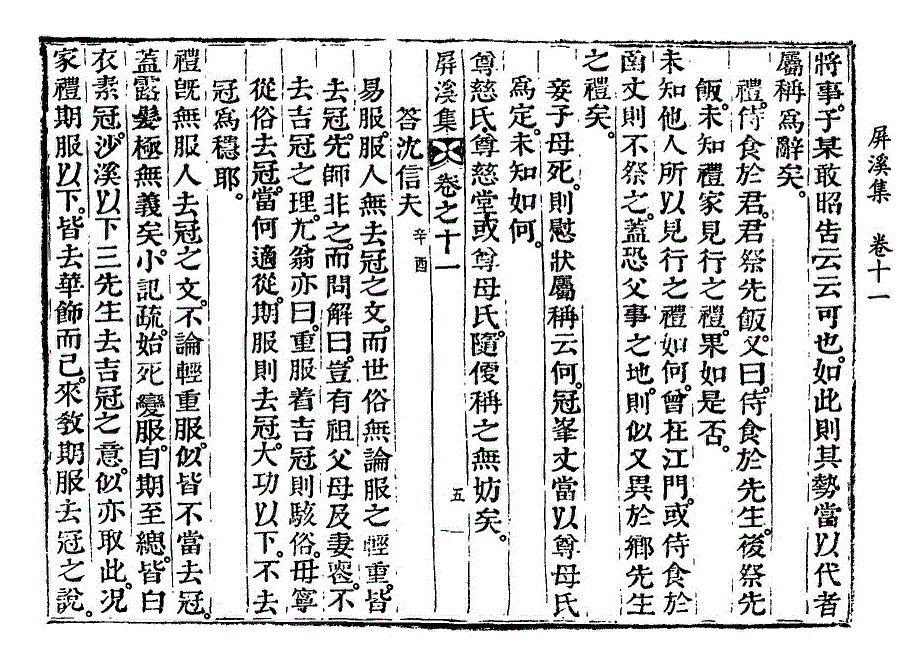 将事。子某敢昭告云云可也。如此则其势当以代者属称为辞矣。
将事。子某敢昭告云云可也。如此则其势当以代者属称为辞矣。礼。侍食于君。君祭先饭。又曰。侍食于先生。后祭先饭。未知礼家见行之礼。果如是否。
未知他人所以见行之礼如何。曾在江门。或侍食于函丈则不祭之。盖恐父事之地。则似又异于乡先生之礼矣。
妾子母死。则慰状属称云何。冠峰丈当以尊母氏为定。未知如何。
尊慈氏,尊慈堂,或尊母氏。随便称之无妨矣。
答沈信夫(辛酉)
易服。服人无去冠之文。而世俗无论服之轻重。皆去冠。先师非之。而问解曰。岂有祖父母及妻丧。不去吉冠之理。尤翁亦曰。重服着吉冠则骇俗。毋宁从俗去冠。当何适从。期服则去冠。大功以下。不去冠为稳耶。
礼既无服人去冠之文。不论轻重服。似皆不当去冠。盖露发极无义矣。小记疏。始死变服。自期至缌。皆白衣素冠。沙溪以下三先生去吉冠之意。似亦取此。况家礼期服以下。皆去华饰而已。来教期服去冠之说。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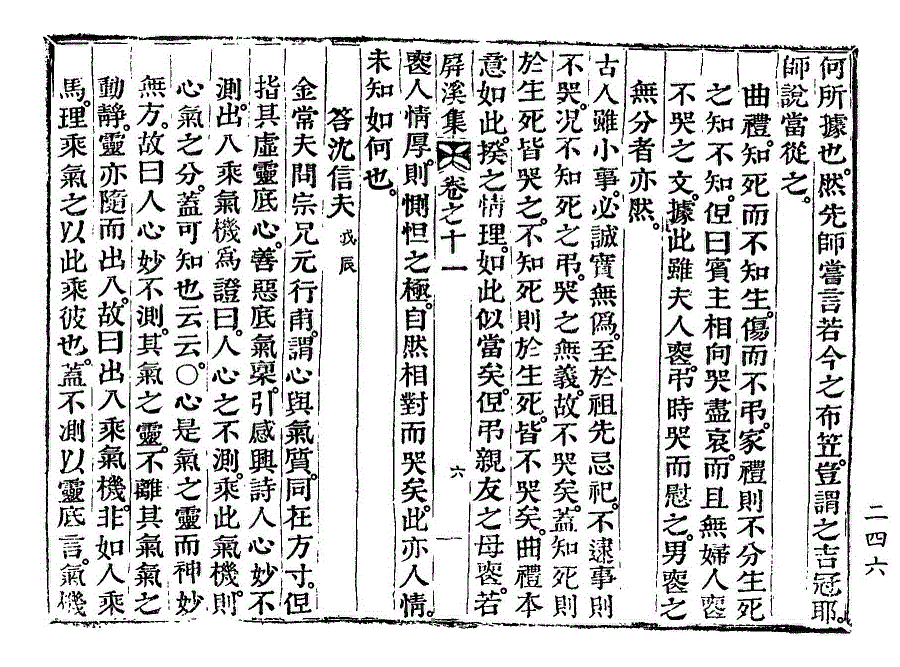 何所据也。然先师尝言若今之布笠。岂谓之吉冠耶。师说当从之。
何所据也。然先师尝言若今之布笠。岂谓之吉冠耶。师说当从之。曲礼。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家礼则不分生死之知不知。但曰宾主相向哭尽哀。而且无妇人丧不哭之文。据此虽夫人丧。吊时哭而慰之。男丧之无分者亦然。
古人虽小事。必诚实无伪。至于祖先忌祀。不逮事则不哭。况不知死之吊。哭之无义。故不哭矣。盖知死则于生死皆哭之。不知死则于生死。皆不哭矣。曲礼本意如此。揆之情理。如此似当矣。但吊亲友之母丧。若丧人情厚。则恻怛之极。自然相对而哭矣。此亦人情。未知如何也。
答沈信夫(戊辰)
金常夫问宗兄元行甫。谓心与气质。同在方寸。但指其虚灵底心。善恶底气禀。引感兴诗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为證曰。人心之不测。乘此气机。则心气之分。盖可知也云云。○心是气之灵而神妙无方。故曰人心妙不测。其气之灵。不离其气气之动静。灵亦随而出入。故曰出入乘气机。非如人乘马。理乘气之以此乘彼也。盖不测以灵底言。气机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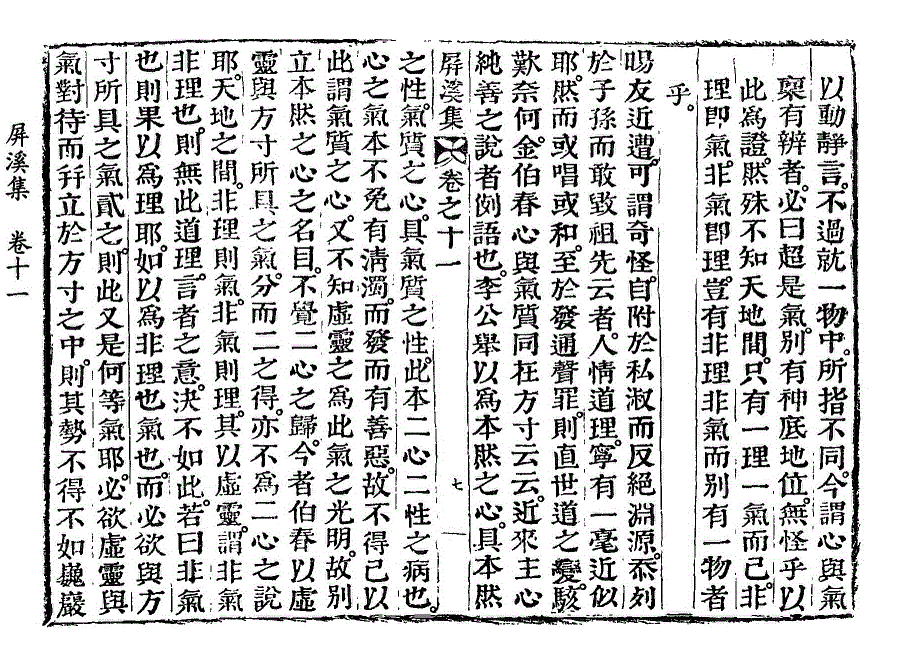 以动静言。不过就一物中。所指不同。今谓心与气禀有辨者。必曰超是气。别有神底地位。无怪乎以此为證。然殊不知天地间。只有一理一气而已。非理即气。非气即理。岂有非理非气而别有一物者乎。
以动静言。不过就一物中。所指不同。今谓心与气禀有辨者。必曰超是气。别有神底地位。无怪乎以此为證。然殊不知天地间。只有一理一气而已。非理即气。非气即理。岂有非理非气而别有一物者乎。旸友近遭。可谓奇怪。自附于私淑而反绝渊源。忝列于子孙而敢毁祖先云者。人情道理。宁有一毫近似耶。然而或唱或和。至于发通声罪。则直世道之变。骇叹奈何。金伯春心与气质同在方寸云云。近来主心纯善之说者例语也。李公举以为本然之心。具本然之性。气质之心。具气质之性。此本二心二性之病也。心之气本不免有清浊。而发而有善恶。故不得已以此谓气质之心。又不知虚灵之为此气之光明。故别立本然之心之名目。不觉二心之归。今者伯春以虚灵与方寸所具之气。分而二之得。亦不为二心之说耶。天地之间。非理则气。非气则理。其以虚灵。谓非气非理也。则无此道理。言者之意。决不如此。若曰非气也则果以为理耶。如以为非理也气也。而必欲与方寸所具之气贰之。则此又是何等气耶。必欲虚灵与气对待而并立于方寸之中。则其势不得不如巍岩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7L 页
 二心之病矣。其引感兴诗者。似亦非朱子本意也。盖圣贤所言心者。有兼理言者。有单指气言者。系辞不测之谓神。正蒙两在故不测。皆指理之乘气者而言也。此所谓妙不测。亦指心之兼理而言。盖以为凡言人心兼理气故不测。而于乘此心气而出入者。可见其不测之妙云也。实如孟子仁义之良心。由夜气之清与否而存亡之也。朱子之意。非于一个气中。分人心与气机。贰之为虚灵与气质而谓两个心也。此皆不究前言。揽作己意之病也。盛书其心与气质贰之之辨则诚好。而以朱子诗人心妙不测。专属气言则恐不然。更商之。
二心之病矣。其引感兴诗者。似亦非朱子本意也。盖圣贤所言心者。有兼理言者。有单指气言者。系辞不测之谓神。正蒙两在故不测。皆指理之乘气者而言也。此所谓妙不测。亦指心之兼理而言。盖以为凡言人心兼理气故不测。而于乘此心气而出入者。可见其不测之妙云也。实如孟子仁义之良心。由夜气之清与否而存亡之也。朱子之意。非于一个气中。分人心与气机。贰之为虚灵与气质而谓两个心也。此皆不究前言。揽作己意之病也。盛书其心与气质贰之之辨则诚好。而以朱子诗人心妙不测。专属气言则恐不然。更商之。答沈信夫(辛未)
气之有动静作为者。是气有自运而然耶。其动静作为者。是理使之然耶。若曰理使之然。则气有善恶。其所谓恶者。亦理使之然耶。若曰恶亦理之使然。则先儒所谓理纯善云者。不亦可疑乎。若曰气有自运。则其所谓恶者。是出于气矣。其区处诚不难矣。然是恶之主张者谁欤。吾知其纯善之理。必不肯从于恶矣。然则其恶气也。果无里面之理。而其空壳之自作动静作为欤。若曰自作动静作为。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8H 页
 则气不必藉理而后为动静作为可知。然则气有自运者明矣。若气有自运。则是理气为二本。而其作为者有互发矣。然则先儒何以二本互发为非欤。又若以理弱气强。理不胜气等语观之。二本互发。其有可据。是果不矛盾于非斥之论欤。(此乃李进士思质书也。请下一转语。)
则气不必藉理而后为动静作为可知。然则气有自运者明矣。若气有自运。则是理气为二本。而其作为者有互发矣。然则先儒何以二本互发为非欤。又若以理弱气强。理不胜气等语观之。二本互发。其有可据。是果不矛盾于非斥之论欤。(此乃李进士思质书也。请下一转语。)送示李生理气说。前者以如此等说承俯询而仰对之。此失草本不可考。而高明想亦不之记有耶。凡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善恶亦气也。而所以善恶亦理也。气之浊而其动也。或之于恶。则理亦随而恶。虽非理之本体。而亦理之本自如此也。气虽千变万化。何莫非理为之主也。若以理之本善。而随气或恶者。谓非理也则不可。又若以理之随气或恶。而疑理之本有恶。则全不是全不是。此理元来无情伪无造作。纯善而已。岂有恶之可言也。但理弱气强。故其使之然者。虽是理而作为者气也。是以气之一善一恶。或有似乎自作为者然。其实善恶皆理之为也。理自理气自气。虽各自别。元不相离。本自浑瀜。酷似一物。今李生之言。似不无太分开。或为二之之病否。虽其一小段文字。而文势之往复曲折。诚有可观。亦可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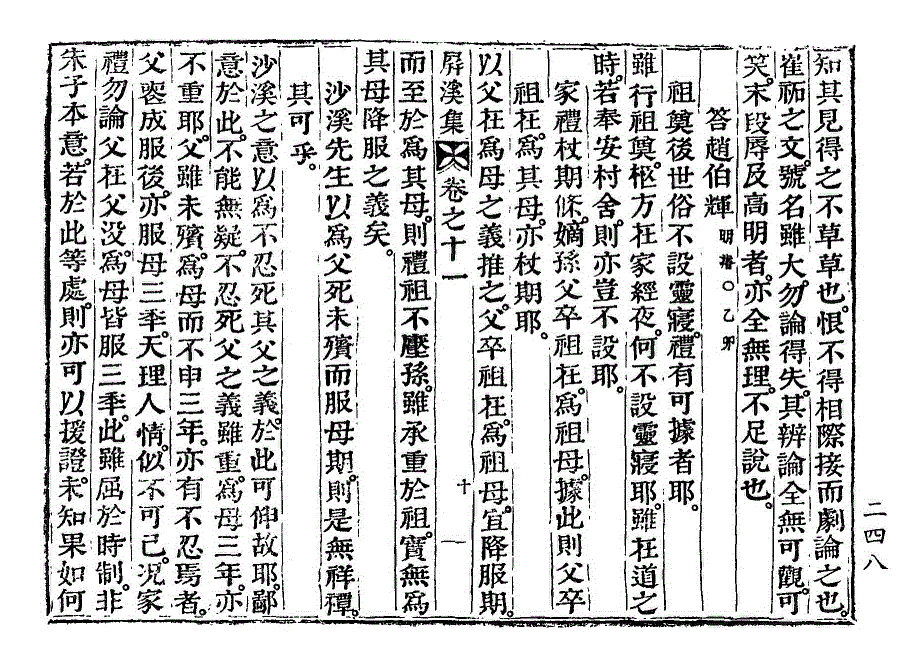 知其见得之不草草也。恨不得相际接而剧论之也。崔祏之文。号名虽大。勿论得失。其辨论全无可观。可笑。末段辱及高明者。亦全无理。不足说也。
知其见得之不草草也。恨不得相际接而剧论之也。崔祏之文。号名虽大。勿论得失。其辨论全无可观。可笑。末段辱及高明者。亦全无理。不足说也。答赵伯辉(明浚○乙卯)
祖奠后世俗不设灵寝。礼有可据者耶。
虽行祖奠。柩方在家经夜。何不设灵寝耶。虽在道之时。若奉安村舍。则亦岂不设耶。
家礼杖期条。嫡孙父卒祖在。为祖母。据此则父卒祖在。为其母。亦杖期耶。
以父在为母之义推之。父卒祖在。为祖母。宜降服期。而至于为其母。则礼祖不压孙。虽承重于祖。实无为其母降服之义矣。
沙溪先生以为父死未殡而服母期。则是无祥禫。其可乎。
沙溪之意以为不忍死其父之义。于此可伸故耶。鄙意于此。不能无疑。不忍死父之义虽重。为母三年。亦不重耶。父虽未殡。为母而不申三年。亦有不忍焉者。父丧成服后。亦服母三年。天理人情。似不可已。况家礼勿论父在父没。为母皆服三年。此虽屈于时制。非朱子本意。若于此等处。则亦可以援證。未知果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9H 页
 也
也家礼杖期条。父卒祖在。为祖母。通典。父死未殡。服祖周。然则嫡孙祖在父卒未殡前。服祖母期。既殡则当服杖期耶。
承重之义甚重。父虽未殡。祖母死。则承重不可已也。
晦日死者。成服当在来月矣。大功以下。当计死月而脱服耶。抑将自成服月而计之耶。
凡服以丧出日计之。不可以成服月论之。
侑食。禫则便是吉祭也。主人自为而拜之如何。卜日时。虽以来月某日告之。然禫日出主时。不为告辞。无乃未安耶。
禫用丧礼。故别于吉礼。自有义意矣。邱仪则有出主告辞。更详之。
父母丧。权窆于家后。三年内迁葬。而破旧墓后。成殡于家内。则与本位灵座。同处一室矣。朝夕上食。并设于殡所及灵座。似为未安。设上食于灵座。而于殡所则只设朝夕奠。未知如何。
迁柩。虽奉于家内。在山时已有别设之灵座。未葬前。此不可辍矣。上食与奠。当设之于新设灵座矣。但以即远之意观之。前日靷奉之柩。不必还奉于家内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49L 页
 改葬时朝夕哭奠。当如新丧。则亦设灵寝盥栉之具耶。
改葬时朝夕哭奠。当如新丧。则亦设灵寝盥栉之具耶。凡所以为之者。一如初丧。则灵寝似亦有之。然衾枕既无之。则虽不能更办。而栉颒奉养之具。宜皆可备矣。
改葬时成殡于家内。则家庙大小祀。固当废行。而至于本位忌祀。则何以为之耶。
虽本位忌祀。未葬前则有奠而无祭。似可只单献无祝。而当设于神主矣。
长子奔丧。在于三月之后。则长子未禫前。其在家兄弟虽已过禫。而犹在吉祭前。不可与平人自同。而又不可观科耶。
来示似当。
答赵伯辉(乙卯)
致云更鼓旧喙。辱斯文无状。骇痛何言。此亦不得尽见章疏。而中间 筵教。大出意虑之外。士林错恶。不无门疏之议。昨见李器甫所报。十九日 筵中。差示悔悟之意。略罪致云。儒疏门疏之议。俱姑止之云。
答赵伯辉(丁巳)
无主人。且无请宾之人。则不可成礼矣。自冠。是孤子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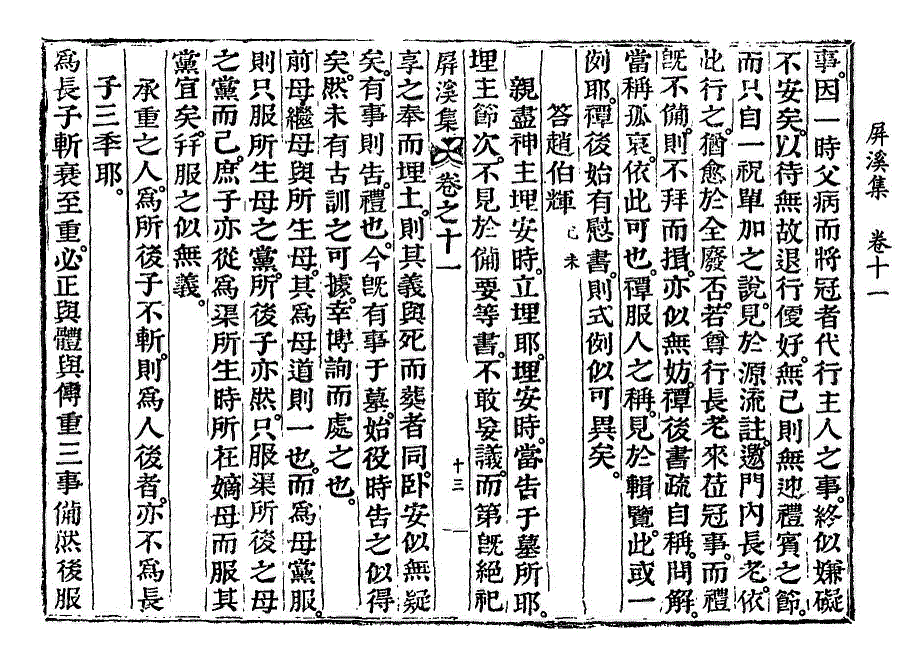 事。因一时父病而将冠者代行主人之事。终似嫌碍不安矣。以待无故退行便好。无已则无迎礼宾之节。而只自一祝单加之说。见于源流注。邀门内长老。依此行之。犹愈于全废否。若尊行长老来莅冠事。而礼既不备。则不拜而揖。亦似无妨。禫后书疏自称。问解。当称孤哀。依此可也。禫服人之称。见于辑览。此或一例耶。禫后始有慰书。则式例似可异矣。
事。因一时父病而将冠者代行主人之事。终似嫌碍不安矣。以待无故退行便好。无已则无迎礼宾之节。而只自一祝单加之说。见于源流注。邀门内长老。依此行之。犹愈于全废否。若尊行长老来莅冠事。而礼既不备。则不拜而揖。亦似无妨。禫后书疏自称。问解。当称孤哀。依此可也。禫服人之称。见于辑览。此或一例耶。禫后始有慰书。则式例似可异矣。答赵伯辉(己未)
亲尽神主埋安时。立埋耶。埋安时。当告于墓所耶。
埋主节次。不见于备要等书。不敢妄议。而第既绝祀享之奉而埋土。则其义与死而葬者同。卧安似无疑矣。有事则告。礼也。今既有事于墓。始役时告之似得矣。然未有古训之可据。幸博询而处之也。
前母,继母与所生母。其为母道则一也。而为母党服。则只服所生母之党。所后子亦然。只服渠所后之母之党而已。庶子亦从为渠所生时所在嫡母而服其党宜矣。并服之似无义。
承重之人。为所后子不斩。则为人后者。亦不为长子三年耶。
为长子斩衰至重。必正与体与传重三事备然后服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0L 页
 之。故郑注曰。三世嫡嫡相承。当服云。所后子非体也。所后子之父。不得为三年。所后子亦不得为其子三年。
之。故郑注曰。三世嫡嫡相承。当服云。所后子非体也。所后子之父。不得为三年。所后子亦不得为其子三年。五六代祖若生存。则皆可齐衰耶。
高祖齐衰三月。礼。高祖以上。皆谓之高祖。虽五六代以上祖。为子孙者。何可无服。若寿如彭祖。则诸子孙之生存者。皆当服齐衰三月。而宗孙则亦当承重斩衰。古礼虽无明文。礼义断如此矣。
答赵伯辉(丙戌)
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
男女有别礼之大节。临绝之时。亦不可忽。故古人知正终之礼者。必麾妇人出去。妇人指妻妾也。妻之于夫。亦何异也。若子女之于父母。弟侄之于姑姊。外孙男女之于外祖父母。似不必用此礼矣。
门下问于先生曰。主祭者遭外党妻党之丧。则以弟侄无服者代行如何。先生答曰。来示然矣。于此不能无疑。
成服前废祭。则所祭亦亲戚者云。今若主人母与妻父母之丧。则以家间情境。固难备需行祭。而以事理言。则所祭先祖。为子与孙曾之妻父母也。以此丧而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1H 页
 阙享。岂不大无义耶。人家有此等事。则遭丧之妇女。移之别室。他子孙妇女来备祭需。无则虽婢仆亦可以备需祭祀。则似不可阙之也。
阙享。岂不大无义耶。人家有此等事。则遭丧之妇女。移之别室。他子孙妇女来备祭需。无则虽婢仆亦可以备需祭祀。则似不可阙之也。先生答蔡徵休曰。三位之祭同日。则鸡鸣后至天明。决难先后行之。然则并设而先献于祖。读祝再拜。次行于祢位而哭之无妨耶。
一庙忌故。或数三位同日。而先后行之。则其势必至于日出。厥明行祀之礼太晚矣。一堂并设。次第献奠。如时祭似无不可。来说正与鄙意无异矣。
先生答金光五曰。亲尽墓祭祝。以行列最尊者为之可矣。又答洪益采曰。宗孙既已代尽。无主祭之义。
礼。五世则宗毁。不复相宗。故远代岁一祭之时。行高者主祝。礼义当然。大宗云者。如别子或如今不迁之位奉祀孙。虽屡世。犹为宗子而主祭也。
先生答朴振河曰。曾见 国恤葬前。私家行葬事。即行虞祭。而卒哭则行于 国葬后。据此则尊从弟妇虞祭。亦似即行矣。卒哭则退行于尊王考葬后似可云云。
祭先重后轻。礼之大节。虞祭则形归窀穸之后。神魂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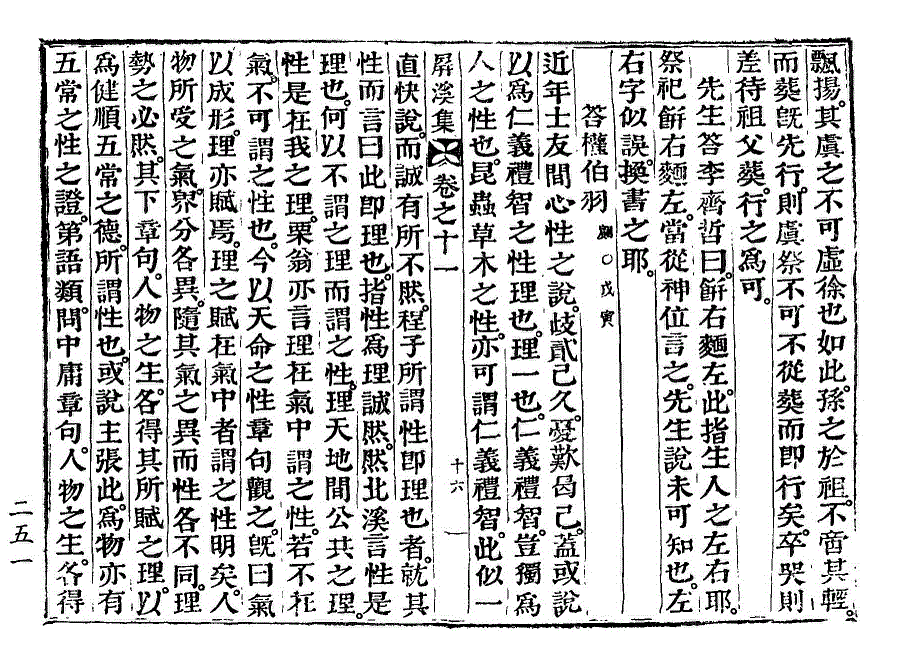 飘扬。其虞之不可虚徐也如此。孙之于祖。不啻其轻。而葬既先行。则虞祭不可不从葬而即行矣。卒哭则差待祖父葬。行之为可。
飘扬。其虞之不可虚徐也如此。孙之于祖。不啻其轻。而葬既先行。则虞祭不可不从葬而即行矣。卒哭则差待祖父葬。行之为可。先生答李齐哲曰。饼右面左。此指生人之左右耶。
祭祀饼右面左。当从神位言之。先生说未可知也。左右字似误。换书之耶。
答权伯羽(䎙○戊寅)
近年士友间心性之说。歧贰已久。忧叹曷已。盖或说以为仁义礼智之性理也。理一也。仁义礼智。岂独为人之性也。昆虫草木之性。亦可谓仁义礼智。此似一直快说。而诚有所不然。程子所谓性即理也者。就其性而言曰此即理也。指性为理诚然。然北溪言性是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理天地间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栗翁亦言理在气中谓之性。若不在气。不可谓之性也。今以天命之性章句观之。既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理之赋在气中者谓之性明矣。人物所受之气。界分各异。随其气之异而性各不同。理势之必然。其下章句。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或说主张此。为物亦有五常之性之證。第语类。问中庸章句。人物之生。各得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2H 页
 云云如何。朱子答曰。马之性健。牛之性顺。健顺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蚁之性义。五常之性也。但禀得来少。不如人之禀得全。问者疑章句之谓人物同禀五常之性。而朱子自释章句之意。谓有偏全之不同者如此。又率性之道章句曰。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当行之路。此两各字。与上各得之各。同一意也。细玩则朱子性字之释人物各异。岂不明白丁宁乎。夫人率仁义礼智之性。为爱敬宜别之道。牛率耕之性。为耕之道。马率驰之性。为驰之道。鸡犬各率鸣吠之性。为鸣吠之道。人物之各正性命。若是其井井不紊。而或说之谓同者。实无异于释氏。狗子有佛性之语。而以人性之最贵。降同于禽兽何也。或说又以为心之灵觉。圣凡无异。盖谓虚灵本体。至虚至灵。是岂圣凡之不同也。此亦不然。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又曰。心气之精爽。盖心气也而盛贮此性。心之发用而性之乘此流行者情也。此所以谓心统性情也。人受天地正通之气。为万物之灵。而心又是正通之精爽。该贮于方寸。为一身之主宰。百骸之血气。皆统属于心而听命焉。故以心谓之天君。盖性虽纯善而无情伪无造作。其敷施运用。全在于心。若圣凡
云云如何。朱子答曰。马之性健。牛之性顺。健顺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蚁之性义。五常之性也。但禀得来少。不如人之禀得全。问者疑章句之谓人物同禀五常之性。而朱子自释章句之意。谓有偏全之不同者如此。又率性之道章句曰。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当行之路。此两各字。与上各得之各。同一意也。细玩则朱子性字之释人物各异。岂不明白丁宁乎。夫人率仁义礼智之性。为爱敬宜别之道。牛率耕之性。为耕之道。马率驰之性。为驰之道。鸡犬各率鸣吠之性。为鸣吠之道。人物之各正性命。若是其井井不紊。而或说之谓同者。实无异于释氏。狗子有佛性之语。而以人性之最贵。降同于禽兽何也。或说又以为心之灵觉。圣凡无异。盖谓虚灵本体。至虚至灵。是岂圣凡之不同也。此亦不然。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又曰。心气之精爽。盖心气也而盛贮此性。心之发用而性之乘此流行者情也。此所以谓心统性情也。人受天地正通之气。为万物之灵。而心又是正通之精爽。该贮于方寸。为一身之主宰。百骸之血气。皆统属于心而听命焉。故以心谓之天君。盖性虽纯善而无情伪无造作。其敷施运用。全在于心。若圣凡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2L 页
 之心。果无异焉。性既同善。心又同美。则人人皆为尧舜。如何而有圣凡之千万等品耶。盖气者从一原而有异。故气之不齐。气之本色。虽气之精粗无限。而粗中也有精粗。精中又也有精粗。分之又分。虽曰极精极美。各自不同。是其阴阳既分。而阴中也有阴阳。阳中又也有阴阳。至于亿兆之无算而自各不同也。是故朱子诵程子之言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天理也。心气也。儒释之分。只在于主理主气之别。孔曾之言德。子思之言命性。孟子之言性善。皆主理之纯善。学者工夫。皆治其心之异而反其性之同。释氏不知性之真。只知气之灵觉运用之妙。不复循性之当然。一任灵觉之自用。终至于猖狂自恣而不自悟也。今之主心善之说者。虽亦斥释氏之不本于性。既曰心之纯善。圣凡皆同。则其自运用自造作之心。必不待诚之者治而变之之功。自当至于圣人不踰矩之域。而其终不然者何也。其又曰。心之气灵觉神明。虽与圣人一般。躯壳血气所禀美恶。各自不同。故此心为其拘蔽。明不能不昏。灵不能不昧。圣凡之不同。非心之有异。只在于气质之有清浊粹驳也。此又不然。心以气之精爽。为一身主宰。居天君之位。其精爽之清粹。
之心。果无异焉。性既同善。心又同美。则人人皆为尧舜。如何而有圣凡之千万等品耶。盖气者从一原而有异。故气之不齐。气之本色。虽气之精粗无限。而粗中也有精粗。精中又也有精粗。分之又分。虽曰极精极美。各自不同。是其阴阳既分。而阴中也有阴阳。阳中又也有阴阳。至于亿兆之无算而自各不同也。是故朱子诵程子之言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天理也。心气也。儒释之分。只在于主理主气之别。孔曾之言德。子思之言命性。孟子之言性善。皆主理之纯善。学者工夫。皆治其心之异而反其性之同。释氏不知性之真。只知气之灵觉运用之妙。不复循性之当然。一任灵觉之自用。终至于猖狂自恣而不自悟也。今之主心善之说者。虽亦斥释氏之不本于性。既曰心之纯善。圣凡皆同。则其自运用自造作之心。必不待诚之者治而变之之功。自当至于圣人不踰矩之域。而其终不然者何也。其又曰。心之气灵觉神明。虽与圣人一般。躯壳血气所禀美恶。各自不同。故此心为其拘蔽。明不能不昏。灵不能不昧。圣凡之不同。非心之有异。只在于气质之有清浊粹驳也。此又不然。心以气之精爽。为一身主宰。居天君之位。其精爽之清粹。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3H 页
 果如圣人之为君。则百体自当从令。血气之浊驳。不能拘蔽。亦如四凶之不敢梗化于尧舜之世也。心是血气之精爽也。随其气之清浊粹驳。而精爽之为君。亦自有清浊粹驳。故血气之感触于天君。而人欲之肆行者。实如桓,灵之昏浊而莽,操之用事也。心之为善为恶。皆心之所自为也。岂如性之无所作为。而因心气之有清浊有所善恶也。如人物性同之论。所不知者物性也。人性之纯善。既皆知之。则诚无碍于明明德之功。至于众人之心。一视如生知之圣。而省存变化之功。不及精爽之地。惟一意尊奉。如中庸之尊德性。则诚大有害于作圣之业。此则不可不知也。但此数端义理。非如语句间文义之比。而论议不咸。深所忧闷。高明欲一闻之。略此布闻。未知盛见以为如何也。
果如圣人之为君。则百体自当从令。血气之浊驳。不能拘蔽。亦如四凶之不敢梗化于尧舜之世也。心是血气之精爽也。随其气之清浊粹驳。而精爽之为君。亦自有清浊粹驳。故血气之感触于天君。而人欲之肆行者。实如桓,灵之昏浊而莽,操之用事也。心之为善为恶。皆心之所自为也。岂如性之无所作为。而因心气之有清浊有所善恶也。如人物性同之论。所不知者物性也。人性之纯善。既皆知之。则诚无碍于明明德之功。至于众人之心。一视如生知之圣。而省存变化之功。不及精爽之地。惟一意尊奉。如中庸之尊德性。则诚大有害于作圣之业。此则不可不知也。但此数端义理。非如语句间文义之比。而论议不咸。深所忧闷。高明欲一闻之。略此布闻。未知盛见以为如何也。与李熙卿(縡○乙卯)
窃谓心固气也。然必合性与气言之。其义乃备。故从古言心。未尝专以气断之。然若就其中单指气言之。则理一也。气二也。圣人众人之心。容有不齐者。此两意。正如论性之有本然气质之殊者。然气之为物。虽有清浊粹驳之不同。而其本则湛然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3L 页
 而已矣。心又气之精爽。而又合理而言之。则不可专着一气字。故其本体之湛然则圣人众人一也。于未发时可见如何。
而已矣。心又气之精爽。而又合理而言之。则不可专着一气字。故其本体之湛然则圣人众人一也。于未发时可见如何。除非心是个气也。其理则性也。其发则情也。分而言之。心与性与情也。各有所指。而若统而言之。举心而性情包在矣。此孟子所谓仁义之良心也。张子所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也。从古圣贤论心。多在此统言分上。是则来教至当矣。第今日所论就分言之中。只指单言气之心。而其气之清浊。有无圣凡同不同之别矣。盖气者不齐也。原二五禀赋之初。则清浊粹驳。千万不同。圣人所禀。二五均停。纯清纯美。其心即均停清美者之精爽。故独能清明纯粹。众人所禀。二五不均。清浊相杂。其心亦不均相杂者之精爽。故强柔昏明。各自不同。万物之中。人之所禀。得其秀而其心灵焉。吾人之中。圣人之禀。又得其最秀而其心最灵。此说已详于蔡氏之传焉。是以上圣清明之心。从其所欲而天理直遂。不踰矩焉。下此以下。则必加澄治之工。浊秽渐消。清明日升而复其性焉。盖众人相杂之心。虽不及圣人之清粹。而惟其精爽之灵昭。故本自活化。不如肝肾脾肺之气一于偏而不可变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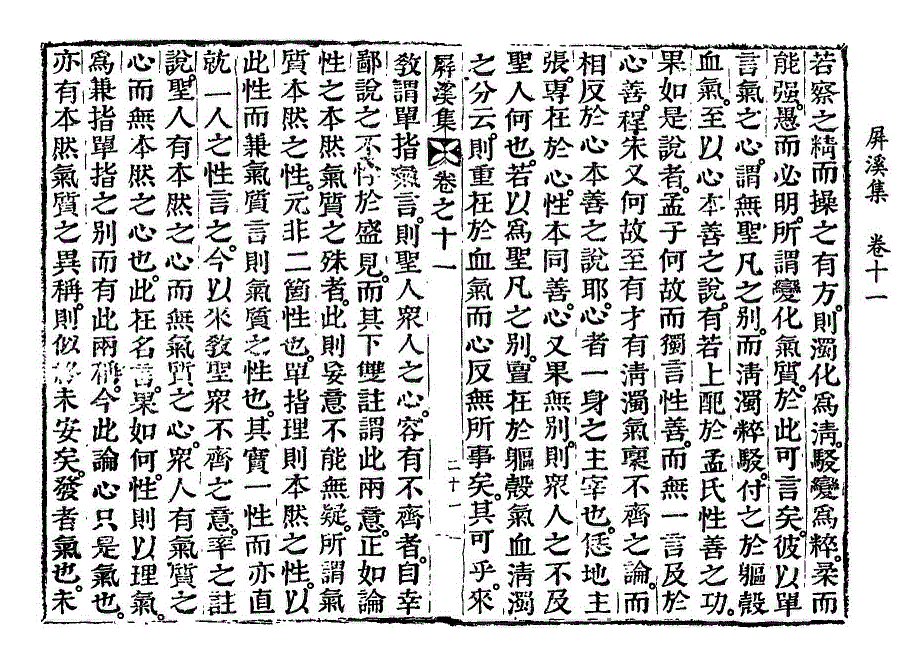 若察之精而操之有方。则浊化为清。驳变为粹。柔而能强。愚而必明。所谓变化气质。于此可言矣。彼以单言气之心。谓无圣凡之别。而清浊粹驳。付之于躯壳血气。至以心本善之说。有若上配于孟氏性善之功。果如是说者。孟子何故而独言性善。而无一言及于心善。程,朱又何故至有才有清浊气禀不齐之论。而相反于心本善之说耶。心者一身之主宰也。恁地主张。专在于心。性本同善。心又果无别。则众人之不及圣人何也。若以为圣凡之别。亶在于躯壳气血清浊之分云。则重在于血气而心反无所事矣。其可乎。来教谓单指气言。则圣人众人之心。容有不齐者。自幸鄙说之不悖于盛见。而其下双注谓此两意。正如论性之本然气质之殊者。此则妄意不能无疑。所谓气质本然之性。元非二个性也。单指理则本然之性。以此性而兼气质言则气质之性也。其实一性而亦直就一人之性言之。今以来教圣众不齐之意。率之注说。圣人有本然之心而无气质之心。众人有气质之心而无本然之心也。此在名言。果如何。性则以理气。为兼指单指之别而有此两称。今此论心只是气也。亦有本然气质之异称。则似终未安矣。发者气也。未
若察之精而操之有方。则浊化为清。驳变为粹。柔而能强。愚而必明。所谓变化气质。于此可言矣。彼以单言气之心。谓无圣凡之别。而清浊粹驳。付之于躯壳血气。至以心本善之说。有若上配于孟氏性善之功。果如是说者。孟子何故而独言性善。而无一言及于心善。程,朱又何故至有才有清浊气禀不齐之论。而相反于心本善之说耶。心者一身之主宰也。恁地主张。专在于心。性本同善。心又果无别。则众人之不及圣人何也。若以为圣凡之别。亶在于躯壳气血清浊之分云。则重在于血气而心反无所事矣。其可乎。来教谓单指气言。则圣人众人之心。容有不齐者。自幸鄙说之不悖于盛见。而其下双注谓此两意。正如论性之本然气质之殊者。此则妄意不能无疑。所谓气质本然之性。元非二个性也。单指理则本然之性。以此性而兼气质言则气质之性也。其实一性而亦直就一人之性言之。今以来教圣众不齐之意。率之注说。圣人有本然之心而无气质之心。众人有气质之心而无本然之心也。此在名言。果如何。性则以理气。为兼指单指之别而有此两称。今此论心只是气也。亦有本然气质之异称。则似终未安矣。发者气也。未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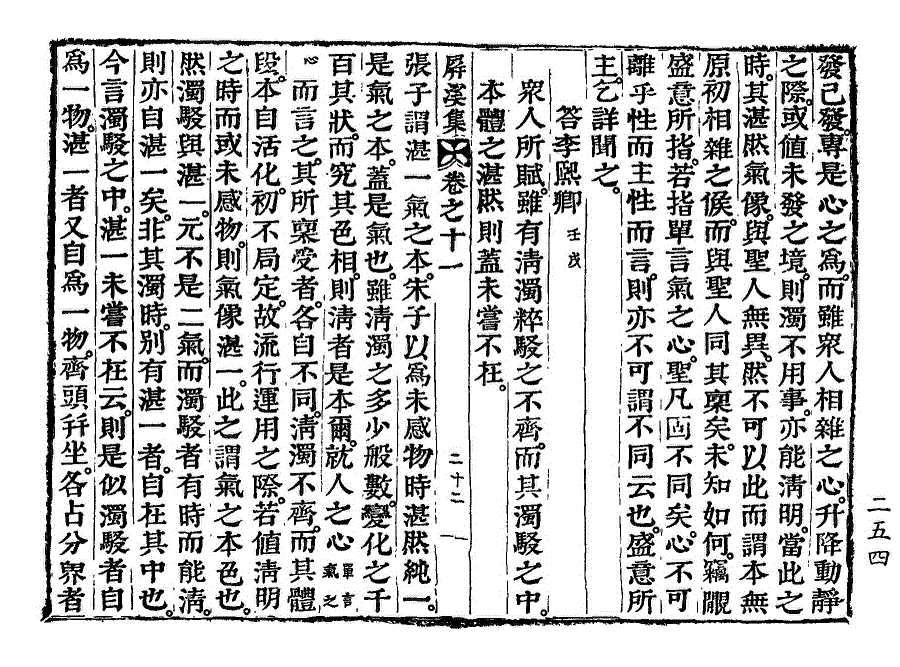 发已发。专是心之为。而虽众人相杂之心。升降动静之际。或值未发之境。则浊不用事。亦能清明。当此之时。其湛然气像。与圣人无异。然不可以此而谓本无原初相杂之候。而与圣人同其禀矣。未知如何。窃覵盛意所指。若指单言气之心。圣凡固不同矣。心不可离乎性而主性而言。则亦不可谓不同云也。盛意所主。乞详闻之。
发已发。专是心之为。而虽众人相杂之心。升降动静之际。或值未发之境。则浊不用事。亦能清明。当此之时。其湛然气像。与圣人无异。然不可以此而谓本无原初相杂之候。而与圣人同其禀矣。未知如何。窃覵盛意所指。若指单言气之心。圣凡固不同矣。心不可离乎性而主性而言。则亦不可谓不同云也。盛意所主。乞详闻之。答李熙卿(壬戌)
众人所赋。虽有清浊粹驳之不齐。而其浊驳之中。本体之湛然则盖未尝不在。
张子谓湛一气之本。朱子以为未感物时湛然纯一。是气之本。盖是气也。虽清浊之多少般数。变化之千百其状。而究其色相。则清者是本尔。就人之心(单言气之心)而言之。其所禀受者。各自不同。清浊不齐。而其体段。本自活化。初不局定。故流行运用之际。若值清明之时而或未感物。则气像湛一。此之谓气之本色也。然浊驳与湛一。元不是二气。而浊驳者有时而能清。则亦自湛一矣。非其浊时。别有湛一者。自在其中也。今言浊驳之中。湛一未尝不在云。则是似浊驳者自为一物。湛一者又自为一物。齐头并坐。各占分界者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5H 页
 然。不然则又如本然之性。包在气质之中者矣。此不可不细商也。栗谷先生曰。花潭以为湛一之气。无物不在。殊不知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之气多有不在者。盖圣人之心。清明纯粹。故未论发与未发。湛一本色。无有不在。众人之心。浊驳之相杂。故常失之动。惟其于未感物时。可见此气像。而众人之有此时节几希也。是以谓湛一之气。多有不在也。盖湛一是纯清之时。此心如有一点浊气。则不可谓湛一之犹在也。未知盛意以为如何。
然。不然则又如本然之性。包在气质之中者矣。此不可不细商也。栗谷先生曰。花潭以为湛一之气。无物不在。殊不知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之气多有不在者。盖圣人之心。清明纯粹。故未论发与未发。湛一本色。无有不在。众人之心。浊驳之相杂。故常失之动。惟其于未感物时。可见此气像。而众人之有此时节几希也。是以谓湛一之气。多有不在也。盖湛一是纯清之时。此心如有一点浊气。则不可谓湛一之犹在也。未知盛意以为如何。愚于中庸首章。每谓未发时不可着气质二字。又曰气质之性。专为众人说。
中庸曰。未发之谓中。其言未发者。心之气之未发用也。于此之时。性则亭亭当当。自然而中矣云。中庸是主天命之性而特言未发时中者。以状性之体段。所重虽在于性。其未发者气也。此气字是心之气。而心之气。即气质中包言者也。虽未发而此气固自在矣。是以朱子以为喜怒哀乐未发时。所谓气质之性。亦在其中。今言未发不可着气质者何也。窃覵盛意。以为若言气质。则不能纯善矣。于其未发湛一之时。不可着此气质字也。第圣人之性。亦囿于气质。若兼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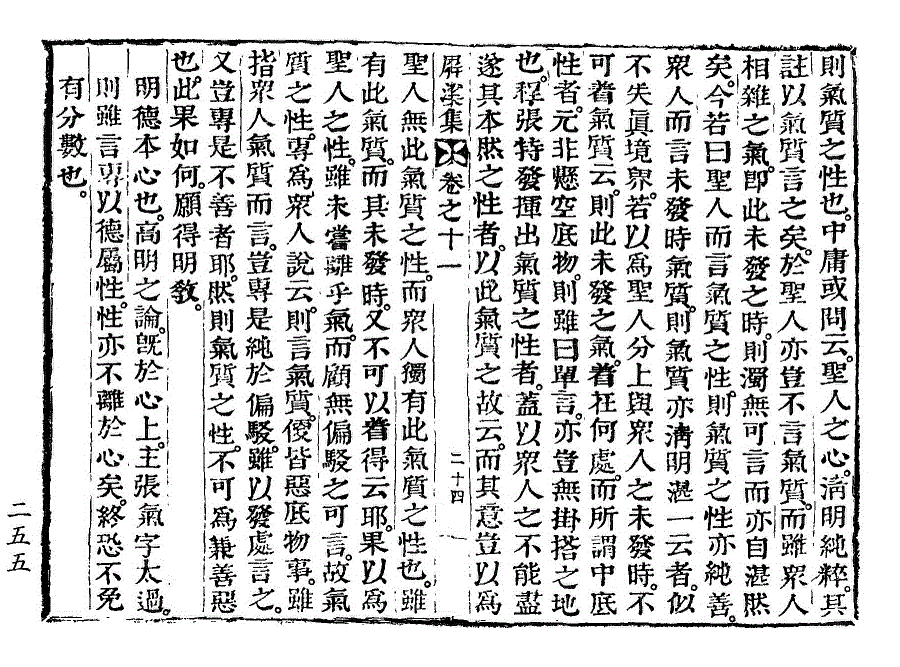 则气质之性也。中庸或问云。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其注以气质言之矣。于圣人亦岂不言气质。而虽众人相杂之气。即此未发之时。则浊无可言而亦自湛然矣。今若曰圣人而言气质之性。则气质之性亦纯善。众人而言未发时气质。则气质亦清明湛一云者。似不失真境界。若以为圣人分上与众人之未发时。不可着气质云。则此未发之气。着在何处。而所谓中底性者。元非悬空底物。则虽曰单言。亦岂无挂搭之地也。程,张特发挥出气质之性者。盖以众人之不能尽遂其本然之性者。以此气质之故云。而其意岂以为圣人无此气质之性。而众人独有此气质之性也。虽有此气质。而其未发时。又不可以着得云耶。果以为圣人之性。虽未尝离乎气。而顾无偏驳之可言。故气质之性。专为众人说云。则言气质。便皆恶底物事。虽指众人气质而言。岂专是纯于偏驳。虽以发处言之。又岂专是不善者耶。然则气质之性。不可为兼善恶也。此果如何。愿得明教。
则气质之性也。中庸或问云。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其注以气质言之矣。于圣人亦岂不言气质。而虽众人相杂之气。即此未发之时。则浊无可言而亦自湛然矣。今若曰圣人而言气质之性。则气质之性亦纯善。众人而言未发时气质。则气质亦清明湛一云者。似不失真境界。若以为圣人分上与众人之未发时。不可着气质云。则此未发之气。着在何处。而所谓中底性者。元非悬空底物。则虽曰单言。亦岂无挂搭之地也。程,张特发挥出气质之性者。盖以众人之不能尽遂其本然之性者。以此气质之故云。而其意岂以为圣人无此气质之性。而众人独有此气质之性也。虽有此气质。而其未发时。又不可以着得云耶。果以为圣人之性。虽未尝离乎气。而顾无偏驳之可言。故气质之性。专为众人说云。则言气质。便皆恶底物事。虽指众人气质而言。岂专是纯于偏驳。虽以发处言之。又岂专是不善者耶。然则气质之性。不可为兼善恶也。此果如何。愿得明教。明德本心也。高明之论。既于心上。主张气字太过。则虽言专以德属性。性亦不离于心矣。终恐不免有分数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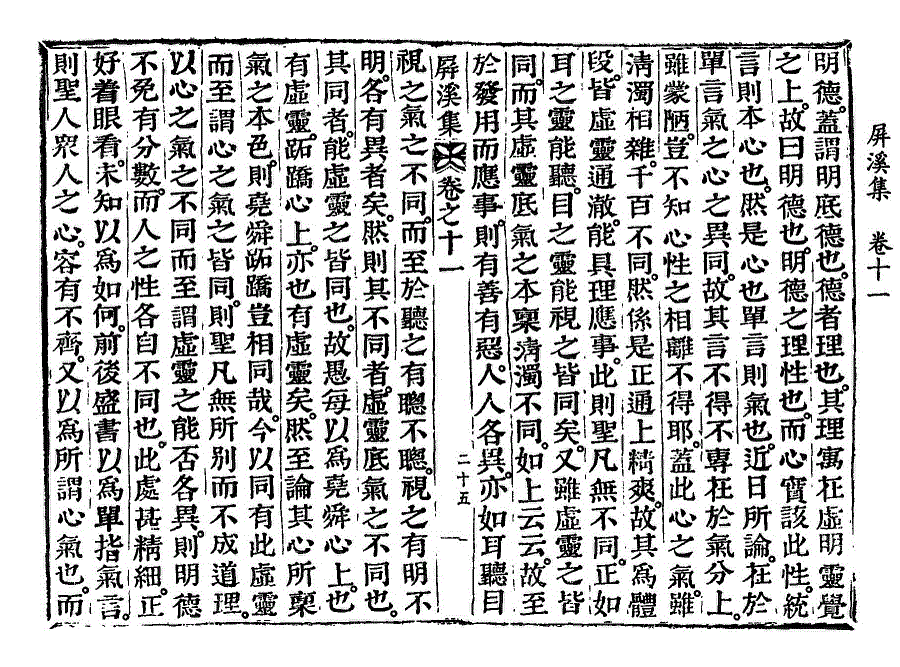 明德。盖谓明底德也。德者理也。其理寓在虚明灵觉之上。故曰明德也。明德之理性也。而心实该此性。统言则本心也。然是心也单言则气也。近日所论。在于单言气之心之异同。故其言不得不专在于气分上。虽蒙陋。岂不知心性之相离不得耶。盖此心之气。虽清浊相杂。千百不同。然系是正通上精爽。故其为体段。皆虚灵通澈。能具理应事。此则圣凡无不同。正如耳之灵能听。目之灵能视之皆同矣。又虽虚灵之皆同。而其虚灵底气之本禀清浊不同。如上云云。故至于发用而应事。则有善有恶。人人各异。亦如耳听目视之气之不同。而至于听之有聪不聪。视之有明不明。各有异者矣。然则其不同者。虚灵底气之不同也。其同者。能虚灵之皆同也。故愚每以为尧舜心上。也有虚灵。蹠蹻心上。亦也有虚灵矣。然至论其心所禀气之本色。则尧舜蹠蹻岂相同哉。今以同有此虚灵而至谓心之气之皆同。则圣凡无所别而不成道理。以心之气之不同而至谓虚灵之能否各异。则明德不免有分数。而人之性各自不同也。此处甚精细。正好着眼看。未知以为如何。前后盛书以为单指气言。则圣人众人之心。容有不齐。又以为所谓心气也。而
明德。盖谓明底德也。德者理也。其理寓在虚明灵觉之上。故曰明德也。明德之理性也。而心实该此性。统言则本心也。然是心也单言则气也。近日所论。在于单言气之心之异同。故其言不得不专在于气分上。虽蒙陋。岂不知心性之相离不得耶。盖此心之气。虽清浊相杂。千百不同。然系是正通上精爽。故其为体段。皆虚灵通澈。能具理应事。此则圣凡无不同。正如耳之灵能听。目之灵能视之皆同矣。又虽虚灵之皆同。而其虚灵底气之本禀清浊不同。如上云云。故至于发用而应事。则有善有恶。人人各异。亦如耳听目视之气之不同。而至于听之有聪不聪。视之有明不明。各有异者矣。然则其不同者。虚灵底气之不同也。其同者。能虚灵之皆同也。故愚每以为尧舜心上。也有虚灵。蹠蹻心上。亦也有虚灵矣。然至论其心所禀气之本色。则尧舜蹠蹻岂相同哉。今以同有此虚灵而至谓心之气之皆同。则圣凡无所别而不成道理。以心之气之不同而至谓虚灵之能否各异。则明德不免有分数。而人之性各自不同也。此处甚精细。正好着眼看。未知以为如何。前后盛书以为单指气言。则圣人众人之心。容有不齐。又以为所谓心气也。而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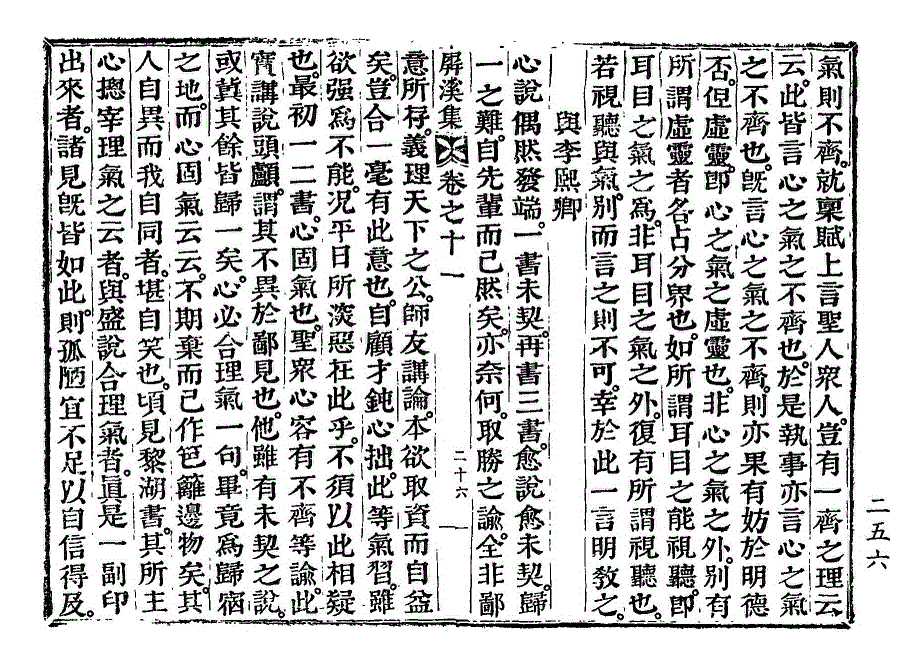 气则不齐。就禀赋上言圣人众人。岂有一齐之理云云。此皆言心之气之不齐也。于是执事亦言心之气之不齐也。既言心之气之不齐。则亦果有妨于明德否。但虚灵。即心之气之虚灵也。非心之气之外。别有所谓虚灵者各占分界也。如所谓耳目之能视听。即耳目之气之为。非耳目之气之外。复有所谓视听也。若视听与气。别而言之则不可。幸于此一言明教之。
气则不齐。就禀赋上言圣人众人。岂有一齐之理云云。此皆言心之气之不齐也。于是执事亦言心之气之不齐也。既言心之气之不齐。则亦果有妨于明德否。但虚灵。即心之气之虚灵也。非心之气之外。别有所谓虚灵者各占分界也。如所谓耳目之能视听。即耳目之气之为。非耳目之气之外。复有所谓视听也。若视听与气。别而言之则不可。幸于此一言明教之。与李熙卿
心说偶然发端。一书未契。再书三书。愈说愈未契。归一之难。自先辈而已然矣。亦奈何。取胜之谕。全非鄙意所存。义理天下之公。师友讲论。本欲取资而自益矣。岂合一毫有此意也。自顾才钝心拙。此等气习。虽欲强为不能。况平日所深恶在此乎。不须以此相疑也。最初一二书。心固气也。圣众心容有不齐等谕。此实讲说头颅。谓其不异于鄙见也。他虽有未契之说。或冀其馀皆归一矣。心必合理气一句。毕竟为归宿之地。而心固气云云。不期弃而已作笆篱边物矣。其人自异而我自同者。堪自笑也。顷见黎湖书。其所主心总宰理气之云者。与盛说合理气者。真是一副印出来者。诸见既皆如此。则孤陋宜不足以自信得及。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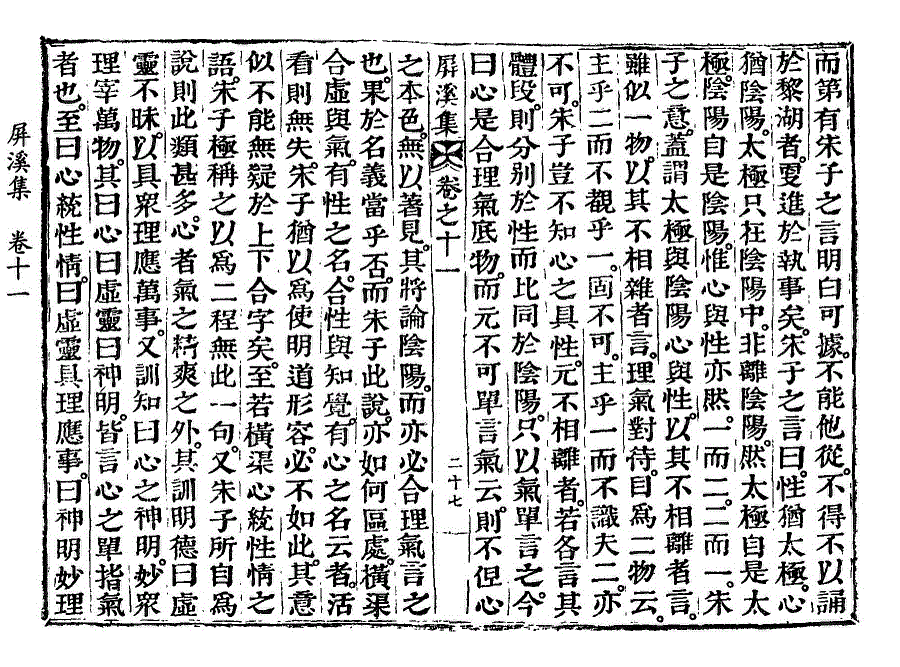 而第有朱子之言明白可据。不能他从。不得不以诵于黎湖者。更进于执事矣。朱子之言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太极只在阴阳中。非离阴阳。然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心与性亦然。一而二。二而一。朱子之意。盖谓太极与阴阳心与性。以其不相离者言。虽似一物。以其不相杂者言。理气对待。目为二物云。主乎二而不睹乎一。固不可。主乎一而不识夫二。亦不可。朱子岂不知心之具性。元不相离者。若各言其体段。则分别于性而比同于阴阳。只以气单言之。今曰心是合理气底物。而元不可单言气云。则不但心之本色。无以著见。其将论阴阳。而亦必合理气言之也。果于名义当乎否。而朱子此说。亦如何区处。横渠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云者。活看则无失。朱子犹以为使明道形容。必不如此。其意似不能无疑于上下合字矣。至若横渠心统性情之语。朱子极称之以为二程无此一句。又朱子所自为说则此类甚多。心者气之精爽之外。其训明德曰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又训知曰心之神明。妙众理宰万物。其曰心曰虚灵曰神明。皆言心之单指气者也。至曰心统性情。曰虚灵具理应事。曰神明妙理
而第有朱子之言明白可据。不能他从。不得不以诵于黎湖者。更进于执事矣。朱子之言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太极只在阴阳中。非离阴阳。然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心与性亦然。一而二。二而一。朱子之意。盖谓太极与阴阳心与性。以其不相离者言。虽似一物。以其不相杂者言。理气对待。目为二物云。主乎二而不睹乎一。固不可。主乎一而不识夫二。亦不可。朱子岂不知心之具性。元不相离者。若各言其体段。则分别于性而比同于阴阳。只以气单言之。今曰心是合理气底物。而元不可单言气云。则不但心之本色。无以著见。其将论阴阳。而亦必合理气言之也。果于名义当乎否。而朱子此说。亦如何区处。横渠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云者。活看则无失。朱子犹以为使明道形容。必不如此。其意似不能无疑于上下合字矣。至若横渠心统性情之语。朱子极称之以为二程无此一句。又朱子所自为说则此类甚多。心者气之精爽之外。其训明德曰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又训知曰心之神明。妙众理宰万物。其曰心曰虚灵曰神明。皆言心之单指气者也。至曰心统性情。曰虚灵具理应事。曰神明妙理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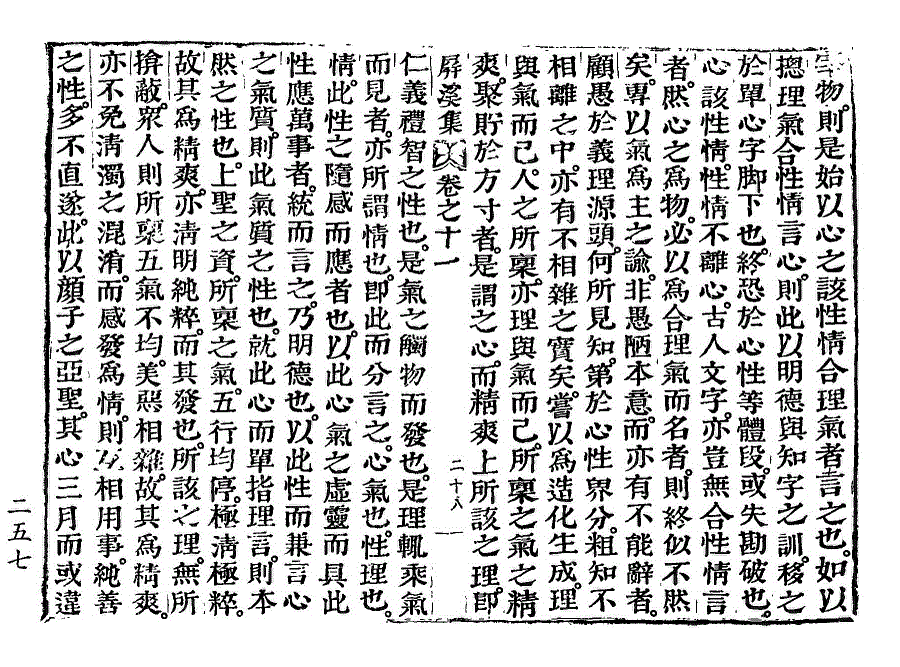 宰物。则是始以心之该性情合理气者言之也。如以总理气合性情言心。则此以明德与知字之训。移之于单心字脚下也。终恐于心性等体段。或失勘破也。心该性情。性情不离心。古人文字。亦岂无合性情言者。然心之为物。必以为合理气而名者。则终似不然矣。专以气为主之谕。非愚陋本意。而亦有不能辞者。顾愚于义理源头。何所见知。第于心性界分。粗知不相离之中。亦有不相杂之实矣。尝以为造化生成。理与气而已。人之所禀。亦理与气而已。所禀之气之精爽。聚贮于方寸者。是谓之心。而精爽上所该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也。是气之触物而发也。是理辄乘气而见者。亦所谓情也。即此而分言之。心气也。性理也。情。此性之随感而应者也。以此心气之虚灵而具此性应万事者。统而言之。乃明德也。以此性而兼言心之气质。则此气质之性也。就此心而单指理言。则本然之性也。上圣之资。所禀之气。五行均停。极清极粹。故其为精爽。亦清明纯粹。而其发也。所该之理。无所掩蔽。众人则所禀五气不均。美恶相杂。故其为精爽。亦不免清浊之混淆。而感发为情。则互相用事。纯善之性。多不直遂。此以颜子之亚圣。其心三月而或违
宰物。则是始以心之该性情合理气者言之也。如以总理气合性情言心。则此以明德与知字之训。移之于单心字脚下也。终恐于心性等体段。或失勘破也。心该性情。性情不离心。古人文字。亦岂无合性情言者。然心之为物。必以为合理气而名者。则终似不然矣。专以气为主之谕。非愚陋本意。而亦有不能辞者。顾愚于义理源头。何所见知。第于心性界分。粗知不相离之中。亦有不相杂之实矣。尝以为造化生成。理与气而已。人之所禀。亦理与气而已。所禀之气之精爽。聚贮于方寸者。是谓之心。而精爽上所该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也。是气之触物而发也。是理辄乘气而见者。亦所谓情也。即此而分言之。心气也。性理也。情。此性之随感而应者也。以此心气之虚灵而具此性应万事者。统而言之。乃明德也。以此性而兼言心之气质。则此气质之性也。就此心而单指理言。则本然之性也。上圣之资。所禀之气。五行均停。极清极粹。故其为精爽。亦清明纯粹。而其发也。所该之理。无所掩蔽。众人则所禀五气不均。美恶相杂。故其为精爽。亦不免清浊之混淆。而感发为情。则互相用事。纯善之性。多不直遂。此以颜子之亚圣。其心三月而或违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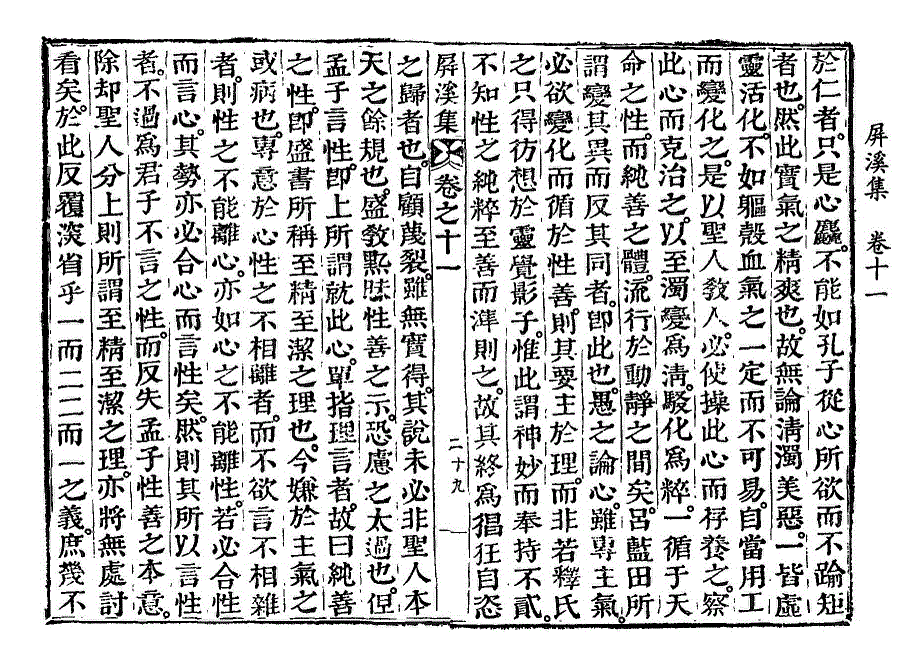 于仁者。只是心粗。不能如孔子从心所欲而不踰矩者也。然此实气之精爽也。故无论清浊美恶。一皆虚灵活化。不如躯壳血气之一定而不可易。自当用工而变化之。是以圣人教人。必使操此心而存养之。察此心而克治之。以至浊变为清。驳化为粹。一循于天命之性。而纯善之体。流行于动静之间矣。吕蓝田所谓变其异而反其同者。即此也。愚之论心。虽专主气。必欲变化而循于性善。则其要主于理。而非若释氏之只得彷想于灵觉影子。惟此谓神妙而奉持不贰。不知性之纯粹至善而准则之。故其终为猖狂自恣之归者也。自顾蔑裂。虽无实得。其说未必非圣人本天之馀规也。盛教䵝昧性善之示。恐虑之太过也。但孟子言性。即上所谓就此心。单指理言者。故曰纯善之性。即盛书所称至精至洁之理也。今嫌于主气之或病也。专意于心性之不相离者。而不欲言不相杂者。则性之不能离心。亦如心之不能离性。若必合性而言心。其势亦必合心而言性矣。然则其所以言性者。不过为君子不言之性。而反失孟子性善之本意。除却圣人分上则所谓至精至洁之理。亦将无处讨看矣。于此反覆深省乎一而二二而一之义。庶几不
于仁者。只是心粗。不能如孔子从心所欲而不踰矩者也。然此实气之精爽也。故无论清浊美恶。一皆虚灵活化。不如躯壳血气之一定而不可易。自当用工而变化之。是以圣人教人。必使操此心而存养之。察此心而克治之。以至浊变为清。驳化为粹。一循于天命之性。而纯善之体。流行于动静之间矣。吕蓝田所谓变其异而反其同者。即此也。愚之论心。虽专主气。必欲变化而循于性善。则其要主于理。而非若释氏之只得彷想于灵觉影子。惟此谓神妙而奉持不贰。不知性之纯粹至善而准则之。故其终为猖狂自恣之归者也。自顾蔑裂。虽无实得。其说未必非圣人本天之馀规也。盛教䵝昧性善之示。恐虑之太过也。但孟子言性。即上所谓就此心。单指理言者。故曰纯善之性。即盛书所称至精至洁之理也。今嫌于主气之或病也。专意于心性之不相离者。而不欲言不相杂者。则性之不能离心。亦如心之不能离性。若必合性而言心。其势亦必合心而言性矣。然则其所以言性者。不过为君子不言之性。而反失孟子性善之本意。除却圣人分上则所谓至精至洁之理。亦将无处讨看矣。于此反覆深省乎一而二二而一之义。庶几不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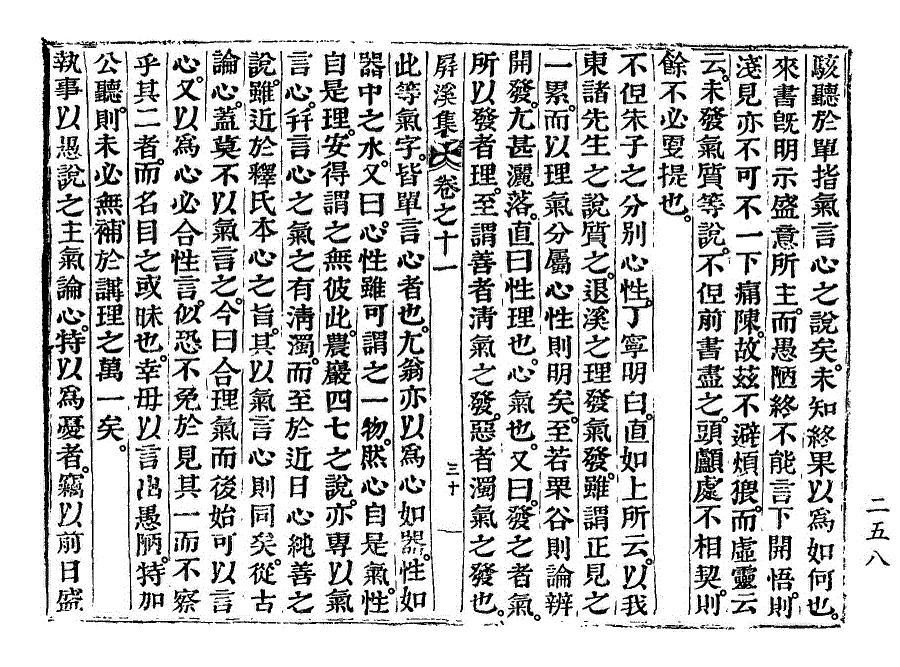 骇听于单指气言心之说矣。未知终果以为如何也。来书既明示盛意所主。而愚陋终不能言下开悟。则浅见亦不可不一下痛陈。故兹不避烦猥。而虚灵云云。未发气质等说。不但前书尽之。头颅处不相契。则馀不必更提也。
骇听于单指气言心之说矣。未知终果以为如何也。来书既明示盛意所主。而愚陋终不能言下开悟。则浅见亦不可不一下痛陈。故兹不避烦猥。而虚灵云云。未发气质等说。不但前书尽之。头颅处不相契。则馀不必更提也。不但朱子之分别心性。丁宁明白。直如上所云。以我东诸先生之说质之。退溪之理发气发。虽谓正见之一累。而以理气分属心性则明矣。至若栗谷则论辨开发。尤甚洒落。直曰性理也。心气也。又曰。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至谓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也。此等气字。皆单言心者也。尤翁亦以为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又曰。心性虽可谓之一物。然心自是气。性自是理。安得谓之无彼此。农岩四七之说。亦专以气言心。并言心之气之有清浊。而至于近日心纯善之说。虽近于释氏本心之旨。其以气言心则同矣。从古论心。盖莫不以气言之。今曰合理气而后始可以言心。又以为心必合性言。似恐不免于见其一而不察乎其二者。而名目之或昧也。幸毋以言出愚陋。特加公听。则未必无补于讲理之万一矣。
执事以愚说之主气论心。特以为忧者。窃以前日盛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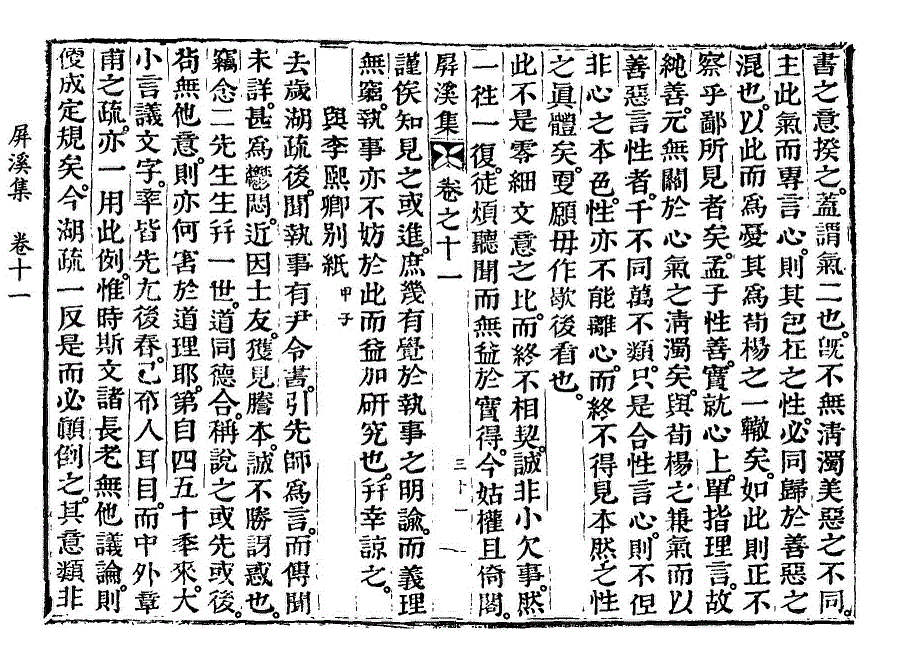 书之意揆之。盖谓气二也。既不无清浊美恶之不同。主此气而专言心。则其包在之性。必同归于善恶之混也。以此而为忧其为荀杨之一辙矣。如此则正不察乎鄙所见者矣。孟子性善。实就心上。单指理言。故纯善。元无关于心气之清浊矣。与荀杨之兼气而以善恶言性者。千不同万不类。只是合性言心。则不但非心之本色。性亦不能离心。而终不得见本然之性之真体矣。更愿毋作歇后看也。
书之意揆之。盖谓气二也。既不无清浊美恶之不同。主此气而专言心。则其包在之性。必同归于善恶之混也。以此而为忧其为荀杨之一辙矣。如此则正不察乎鄙所见者矣。孟子性善。实就心上。单指理言。故纯善。元无关于心气之清浊矣。与荀杨之兼气而以善恶言性者。千不同万不类。只是合性言心。则不但非心之本色。性亦不能离心。而终不得见本然之性之真体矣。更愿毋作歇后看也。此不是零细文意之比。而终不相契。诚非小欠事。然一往一复。徒烦听闻而无益于实得。今姑权且倚阁。谨俟知见之或进。庶几有觉于执事之明谕。而义理无穷。执事亦不妨于此而益加研究也。并幸谅之。
与李熙卿别纸(甲子)
去岁湖疏后。闻执事有尹令书。引先师为言。而传闻未详。甚为郁闷。近因士友。获见誊本。诚不胜讶惑也。窃念二先生生并一世。道同德合。称说之或先或后。苟无他意。则亦何害于道理耶。第自四五十年来。大小言议文字。率皆先尤后春。已布人耳目。而中外章甫之疏。亦一用此例。惟时斯文诸长老无他议论。则便成定规矣。今湖疏一反是而必颠倒之。其意类非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59L 页
 偶然者。似此议论。固不可崇长。而执事既许以一读爽然。又称以好文字。而至引先师温对之说。以證其所执之非无稽者抑何也。温对云云。诚有其说。先师平日父视尤翁。其以体尤翁兄事之心及其并称臣师而为言。则以年而先后者。在先师分上固也。至于乡祠位次。亦没而祭社之意。则盖从世代年齿之序也。若后人之尚论者义又不同。岂可因此为例乎。以当日 筵奏言之。至陈相传旨诀春秋大义。则单举尤翁。此亦非故为也。其或先或单而各自有义也。先师之意。只如上所云。则其先后之称。在子孙。何所喜愠。是时宋景徽从兄弟犹无恙。而其后承皆以为元无愠意。此必闻之于执事者误也。今以先师所以先后者。真若可以喜愠。而彼疏所言。又受先师之意。真又不可斥以无稽者然。则诚大有失于先师本旨矣。昔朱夫子于延平及刘胡诸公。一事之矣。至于论赞之际。不可以一事之故而全无别焉。先师于二先生。亦皆师事之矣。其尊尚春翁。岂不至也。然视尤翁。不能无间。观其祭二先生文。可知其他。如门人答问及所自著文字。可见其本意非一二矣。曾不究此。乃以颠倒轩轾之论者。援先师为言。而及闵友书出。则直
偶然者。似此议论。固不可崇长。而执事既许以一读爽然。又称以好文字。而至引先师温对之说。以證其所执之非无稽者抑何也。温对云云。诚有其说。先师平日父视尤翁。其以体尤翁兄事之心及其并称臣师而为言。则以年而先后者。在先师分上固也。至于乡祠位次。亦没而祭社之意。则盖从世代年齿之序也。若后人之尚论者义又不同。岂可因此为例乎。以当日 筵奏言之。至陈相传旨诀春秋大义。则单举尤翁。此亦非故为也。其或先或单而各自有义也。先师之意。只如上所云。则其先后之称。在子孙。何所喜愠。是时宋景徽从兄弟犹无恙。而其后承皆以为元无愠意。此必闻之于执事者误也。今以先师所以先后者。真若可以喜愠。而彼疏所言。又受先师之意。真又不可斥以无稽者然。则诚大有失于先师本旨矣。昔朱夫子于延平及刘胡诸公。一事之矣。至于论赞之际。不可以一事之故而全无别焉。先师于二先生。亦皆师事之矣。其尊尚春翁。岂不至也。然视尤翁。不能无间。观其祭二先生文。可知其他。如门人答问及所自著文字。可见其本意非一二矣。曾不究此。乃以颠倒轩轾之论者。援先师为言。而及闵友书出。则直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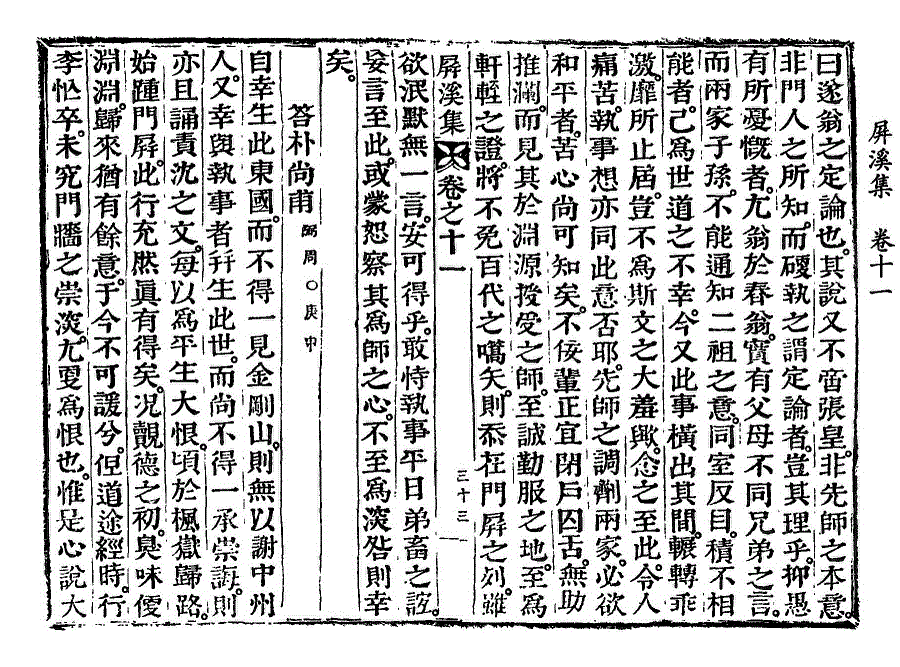 曰遂翁之定论也。其说又不啻张皇。非先师之本意。非门人之所知。而硬执之谓定论者。岂其理乎。抑愚有所忧慨者。尤翁于春翁。实有父母不同兄弟之言。而两家子孙。不能通知二祖之意。同室反目。积不相能者。已为世道之不幸。今又此事横出其间。辗转乖激。靡所止届。岂不为斯文之大羞欤。念之至此。令人痛苦。执事想亦同此意否耶。先师之调剂两家。必欲和平者。苦心尚可知矣。不佞辈正宜闭户囚舌。无助推澜。而见其于渊源授受之师。至诚勤服之地。至为轩轾之證。将不免百代之
曰遂翁之定论也。其说又不啻张皇。非先师之本意。非门人之所知。而硬执之谓定论者。岂其理乎。抑愚有所忧慨者。尤翁于春翁。实有父母不同兄弟之言。而两家子孙。不能通知二祖之意。同室反目。积不相能者。已为世道之不幸。今又此事横出其间。辗转乖激。靡所止届。岂不为斯文之大羞欤。念之至此。令人痛苦。执事想亦同此意否耶。先师之调剂两家。必欲和平者。苦心尚可知矣。不佞辈正宜闭户囚舌。无助推澜。而见其于渊源授受之师。至诚勤服之地。至为轩轾之證。将不免百代之答朴尚甫(弼周○庚申)
自幸生此东国。而不得一见金刚山。则无以谢中州人。又幸与执事者并生此世。而尚不得一承崇诲。则亦且诵责沈之文。每以为平生大恨。顷于枫岳归路。始踵门屏。此行充然真有得矣。况觌德之初。臭味便渊渊。归来犹有馀意。于今不可谖兮。但道途经时。行李忙卒。未究门墙之崇深。尤更为恨也。惟是心说大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60L 页
 体不相背。此盖原头大论。而实幸前日鄙见不至全弃也。窃想盛论于此必有著于文字者。何以则可得一赏。或因竹西而不惮投示。卒开迷蒙否。
体不相背。此盖原头大论。而实幸前日鄙见不至全弃也。窃想盛论于此必有著于文字者。何以则可得一赏。或因竹西而不惮投示。卒开迷蒙否。